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x 页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杂著
杂著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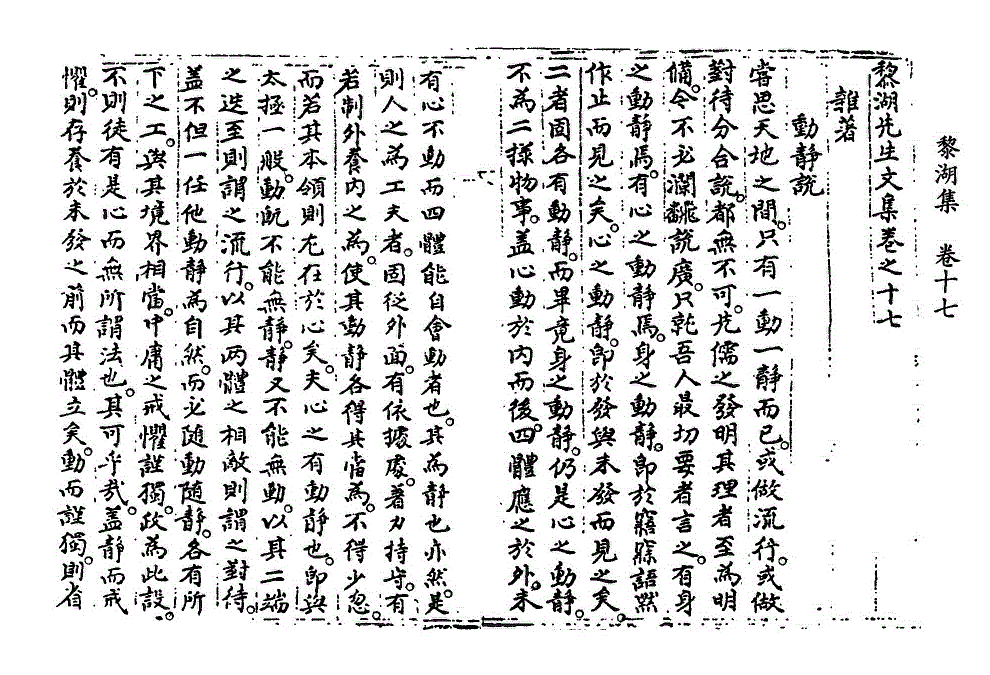 动静说
动静说尝思天地之间。只有一动一静而已。或做流行。或做对待分合说。都无不可。先儒之发明其理者至为明备。今不必澜翻说广。只就吾人最切要者言之。有身之动静焉。有心之动静焉。身之动静。即于寤寐语默作止而见之矣。心之动静。即于发与未发而见之矣。二者固各有动静。而毕竟身之动静。仍是心之动静。不为二㨾物事。盖心动于内而后。四体应之于外。未有心不动而四体能自会动者也。其为静也亦然。是则人之为工夫者。固从外面。有依据处。着力持守。有若制外养内之为。使其动静各得其当为。不得少忽。而若其本领则尤在于心矣。夫心之有动静也。即与太极一般。动既不能无静。静又不能无动。以其二端之迭至则谓之流行。以其两体之相敌则谓之对待。盖不但一任他动静为自然。而必随动随静。各有所下之工。与其境界相当。中庸之戒惧谨独。政为此设。不则徒有是心而无所谓法也。其可乎哉。盖静而戒惧。则存养于未发之前而其体立矣。动而谨独。则省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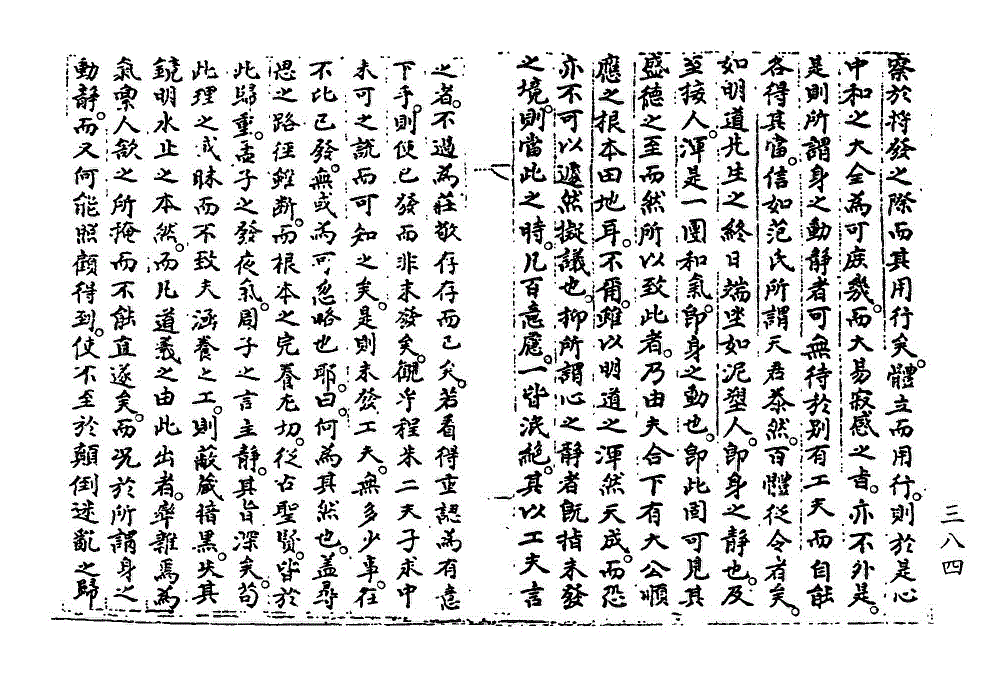 察于将发之际而其用行矣。体立而用行。则于是心中和之大全为可庶几。而大易寂感之旨。亦不外是。是则所谓身之动静者可无待于别有工夫而自能各得其当。信如范氏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者矣。如明道先生之终日端坐如泥塑人。即身之静也。及至接人。浑是一团和气。即身之动也。即此固可见其盛德之至而然所以致此者。乃由夫合下有大公顺应之根本田地耳。不尔。虽以明道之浑然天成。而恐亦不可以遽然拟议也。抑所谓心之静者既指未发之境。则当此之时。凡百意虑。一皆泯绝。其以工夫言之者。不过为庄敬存存而已矣。若看得重认为有意下手。则便已发而非未发矣。观乎程朱二夫子求中未可之说而可知之矣。是则未发工夫。无多少事。在不比已发。无或为可忽略也耶。曰。何为其然也。盖寻思之路径虽断。而根本之完养尤切。从古圣贤。皆于此归重。孟子之发夜气。周子之言主静。其旨深矣。苟此理之或昧而不致夫涵养之工。则蔽藏揞黑。失其镜明水止之本然。而凡道义之由此出者。率杂焉为气禀人欲之所掩而不能直遂矣。而况于所谓身之动静。而又何能照顾得到。使不至于颠倒迷乱之归
察于将发之际而其用行矣。体立而用行。则于是心中和之大全为可庶几。而大易寂感之旨。亦不外是。是则所谓身之动静者可无待于别有工夫而自能各得其当。信如范氏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者矣。如明道先生之终日端坐如泥塑人。即身之静也。及至接人。浑是一团和气。即身之动也。即此固可见其盛德之至而然所以致此者。乃由夫合下有大公顺应之根本田地耳。不尔。虽以明道之浑然天成。而恐亦不可以遽然拟议也。抑所谓心之静者既指未发之境。则当此之时。凡百意虑。一皆泯绝。其以工夫言之者。不过为庄敬存存而已矣。若看得重认为有意下手。则便已发而非未发矣。观乎程朱二夫子求中未可之说而可知之矣。是则未发工夫。无多少事。在不比已发。无或为可忽略也耶。曰。何为其然也。盖寻思之路径虽断。而根本之完养尤切。从古圣贤。皆于此归重。孟子之发夜气。周子之言主静。其旨深矣。苟此理之或昧而不致夫涵养之工。则蔽藏揞黑。失其镜明水止之本然。而凡道义之由此出者。率杂焉为气禀人欲之所掩而不能直遂矣。而况于所谓身之动静。而又何能照顾得到。使不至于颠倒迷乱之归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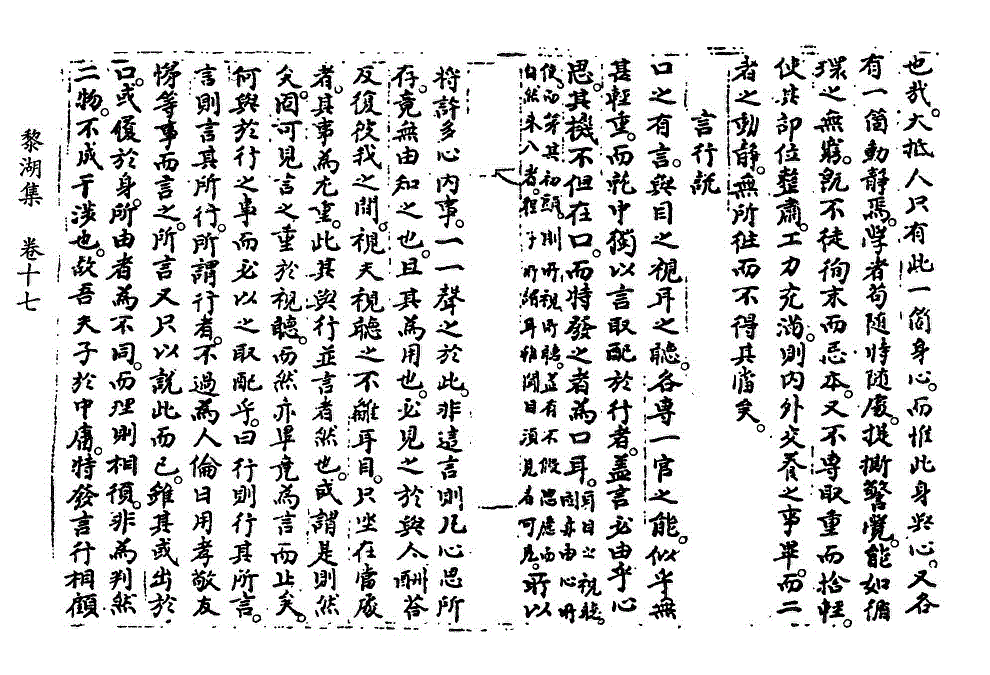 也哉。大抵人只有此一个身心。而惟此身与心。又各有一个动静焉。学者苟随时随处。提撕警觉。能如循环之无穷。既不徒徇末而忘本。又不专取重而舍轻。使其部位整肃。工力充满。则内外交养之事毕。而二者之动静。无所往而不得其当矣。
也哉。大抵人只有此一个身心。而惟此身与心。又各有一个动静焉。学者苟随时随处。提撕警觉。能如循环之无穷。既不徒徇末而忘本。又不专取重而舍轻。使其部位整肃。工力充满。则内外交养之事毕。而二者之动静。无所往而不得其当矣。言行说
口之有言。与目之视耳之听。各专一官之能。似乎无甚轻重。而就中独以言取配于行者。盖言必由乎心思。其机不但在口。而特发之者为口耳。(耳目之视听。固亦由心所使。而第其初头。则所视所听。盖有不假思虑而自然来入者。程子所谓耳虽闻目须见者可见。)所以将许多心内事。一一声之于此。非这言则凡心思所存。竟无由知之也。且其为用也。必见之于与人酬答反复彼我之间。视夫视听之不离耳目。只坐在当处者。其事为尤重。此其与行并言者然也。或谓是则然矣。固可见言之重于视听。而然亦毕竟为言而止矣。何与于行之事而必以之取配乎。曰行则行其所言。言则言其所行。所谓行者。不过为人伦日用孝敬友悌等事而言之。所言又只以说此而已。虽其或出于口。或履于身。所由者为不同。而理则相须。非为判然二物。不成干涉也。故吾夫子于中庸。特发言行相顾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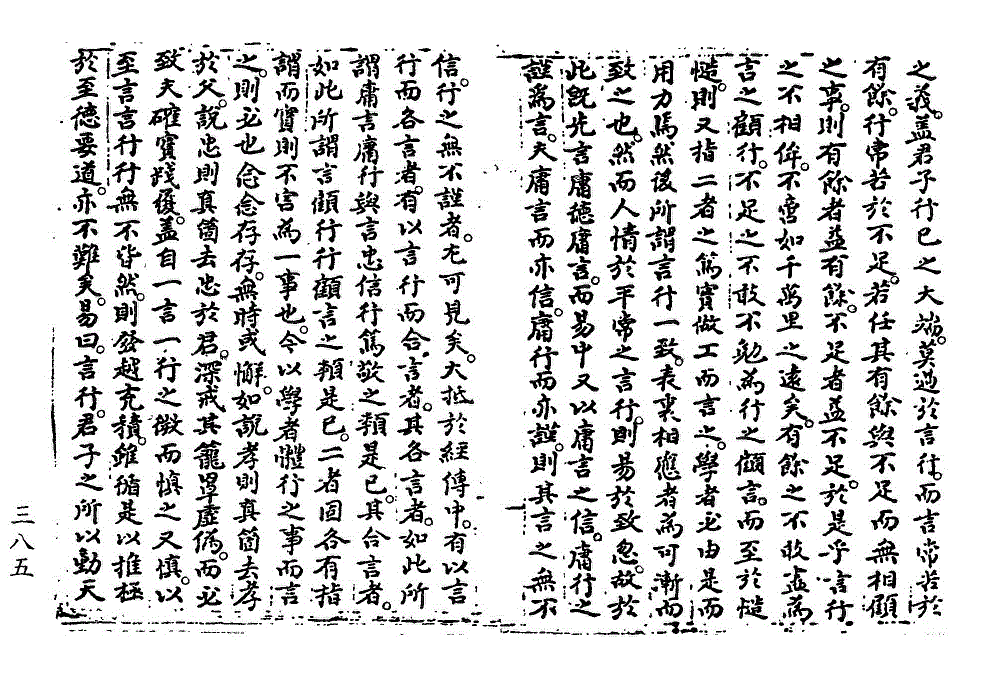 之义。盖君子行己之大端。莫过于言行。而言常苦于有馀。行常苦于不足。若任其有馀与不足而无相顾之事。则有馀者益有馀。不足者益不足。于是乎言行之不相侔。不啻如千万里之远矣。有馀之不敢尽为言之顾行。不足之不敢不勉为行之顾言。而至于慥慥。则又指二者之笃实做工而言之。学者必由是而用力焉然后所谓言行一致。表里相应者为可渐而致之也。然而人情于平常之言行。则易于致忽。故于此既先言庸德庸言。而易中又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为言。夫庸言而亦信。庸行而亦谨。则其言之无不信。行之无不谨者。尤可见矣。大抵于经传中。有以言行而各言者。有以言行而合言者。其各言者。如此所谓庸言庸行与言忠信行笃敬之类是已。其合言者。如此所谓言顾行行顾言之类是已。二者固各有指谓而实则不害为一事也。今以学者体行之事而言之。则必也念念存存。无时或懈。如说孝则真个去孝于父。说忠则真个去忠于君。深戒其笼罩虚伪。而必致夫确实践履。盖自一言一行之微而慎之又慎。以至言言行行无不皆然。则发越充积。虽循是以推极于至德要道。亦不难矣。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
之义。盖君子行己之大端。莫过于言行。而言常苦于有馀。行常苦于不足。若任其有馀与不足而无相顾之事。则有馀者益有馀。不足者益不足。于是乎言行之不相侔。不啻如千万里之远矣。有馀之不敢尽为言之顾行。不足之不敢不勉为行之顾言。而至于慥慥。则又指二者之笃实做工而言之。学者必由是而用力焉然后所谓言行一致。表里相应者为可渐而致之也。然而人情于平常之言行。则易于致忽。故于此既先言庸德庸言。而易中又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为言。夫庸言而亦信。庸行而亦谨。则其言之无不信。行之无不谨者。尤可见矣。大抵于经传中。有以言行而各言者。有以言行而合言者。其各言者。如此所谓庸言庸行与言忠信行笃敬之类是已。其合言者。如此所谓言顾行行顾言之类是已。二者固各有指谓而实则不害为一事也。今以学者体行之事而言之。则必也念念存存。无时或懈。如说孝则真个去孝于父。说忠则真个去忠于君。深戒其笼罩虚伪。而必致夫确实践履。盖自一言一行之微而慎之又慎。以至言言行行无不皆然。则发越充积。虽循是以推极于至德要道。亦不难矣。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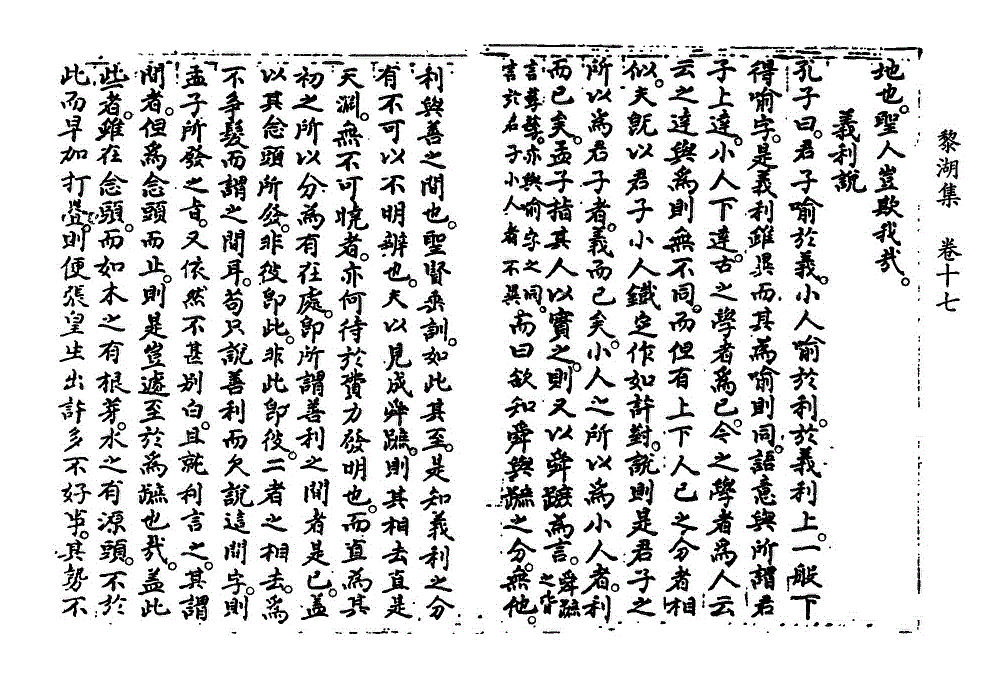 地也。圣人岂欺我哉。
地也。圣人岂欺我哉。义利说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义利上。一般下得喻字。是义利虽异而其为喻则同。语意与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云云之达与为则无不同。而但有上下人己之分者相似。夫既以君子小人铁定作如许对。说则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义而已矣。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者。利而已矣。孟子指其人以实之。则又以舜蹠为言。(舜蹠之皆言孳孳。亦与喻字之同。言于君子小人者不异。)而曰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圣贤垂训。如此其至。是知义利之分有不可以不明辨也。夫以见成舜蹠。则其相去直是天渊。无不可晓者。亦何待于费力发明也。而直为其初之所以分为有在处。即所谓善利之间者是已。盖以其念头所发。非彼即此。非此即彼。二者之相去。为不争发而谓之间耳。苟只说善利而欠说这间字。则孟子所发之旨。又依然不甚别白。且就利言之。其谓间者。但为念头而止。则是岂遽至于为蹠也哉。盖此些者。虽在念头。而如木之有根芽。水之有源头。不于此而早加打叠。则便张皇生出许多不好事。其势不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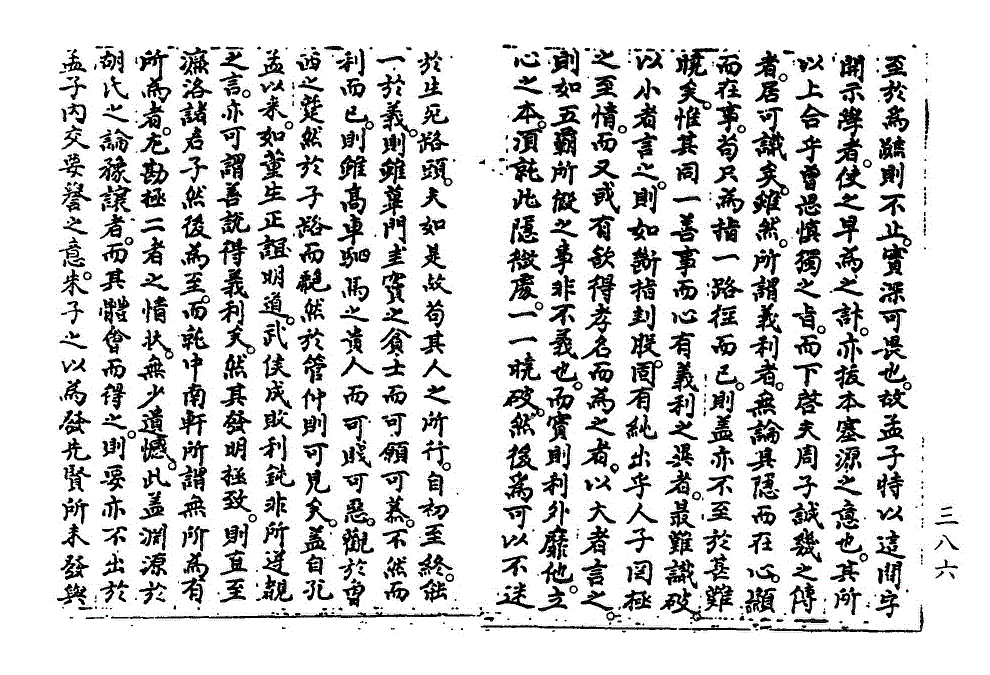 至于为蹠则不止。实深可畏也。故孟子特以这间字开示学者。使之早为之计。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其所以上合乎曾思慎独之旨。而下启夫周子诚几之传者。居可识矣。虽然。所谓义利者。无论其隐而在心。显而在事。苟只为指一路径而已。则盖亦不至于甚难晓矣。惟其同一善事而心有义利之异者。最难识破。以小者言之。则如断指刲股。固有纯出乎人子罔极之至情。而又或有欲得孝名而为之者。以大者言之。则如五霸所假之事非不义也。而实则利外靡他。立心之本。须就此隐微处。一一晓破。然后为可以不迷于生死路头。夫如是故苟其人之所行。自初至终。能一于义。则虽荜门圭窦之贫士而可愿可慕。不然而利而已。则虽高车驷马之贵人而可贱可恶。观于曾西之蹴然于子路而绝然于管仲则可见矣。盖自孔孟以来。如董生正谊明道。武侯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之言。亦可谓善说得义利矣。然其发明极致。则直至濂洛诸君子然后为至。而就中南轩所谓无所为有所为者。尤勘极二者之情状。无少遗憾。此盖渊源于胡氏之论豫让者。而其体会而得之。则要亦不出于孟子内交要誉之意。朱子之以为发先贤所未发与
至于为蹠则不止。实深可畏也。故孟子特以这间字开示学者。使之早为之计。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其所以上合乎曾思慎独之旨。而下启夫周子诚几之传者。居可识矣。虽然。所谓义利者。无论其隐而在心。显而在事。苟只为指一路径而已。则盖亦不至于甚难晓矣。惟其同一善事而心有义利之异者。最难识破。以小者言之。则如断指刲股。固有纯出乎人子罔极之至情。而又或有欲得孝名而为之者。以大者言之。则如五霸所假之事非不义也。而实则利外靡他。立心之本。须就此隐微处。一一晓破。然后为可以不迷于生死路头。夫如是故苟其人之所行。自初至终。能一于义。则虽荜门圭窦之贫士而可愿可慕。不然而利而已。则虽高车驷马之贵人而可贱可恶。观于曾西之蹴然于子路而绝然于管仲则可见矣。盖自孔孟以来。如董生正谊明道。武侯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之言。亦可谓善说得义利矣。然其发明极致。则直至濂洛诸君子然后为至。而就中南轩所谓无所为有所为者。尤勘极二者之情状。无少遗憾。此盖渊源于胡氏之论豫让者。而其体会而得之。则要亦不出于孟子内交要誉之意。朱子之以为发先贤所未发与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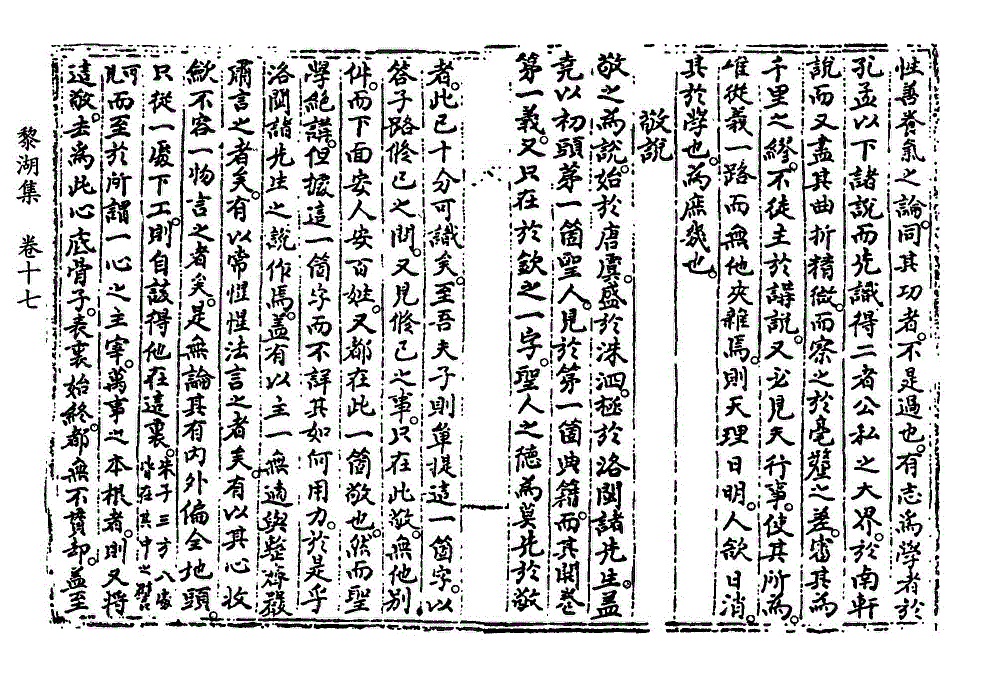 性善养气之论。同其功者。不是过也。有志为学者于孔孟以下诸说而先识得二者公私之大界。于南轩说而又尽其曲折精微。而察之于毫釐之差。审其为千里之缪。不徒主于讲说。又必见夫行事。使其所为。唯从义一路而无他夹杂焉。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其于学也。为庶几也。
性善养气之论。同其功者。不是过也。有志为学者于孔孟以下诸说而先识得二者公私之大界。于南轩说而又尽其曲折精微。而察之于毫釐之差。审其为千里之缪。不徒主于讲说。又必见夫行事。使其所为。唯从义一路而无他夹杂焉。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其于学也。为庶几也。敬说
敬之为说。始于唐虞。盛于洙泗。极于洛闽诸先生。盖尧以初头第一个圣人。见于第一个典籍。而其开卷第一义。又只在于钦之一字。圣人之德为莫先于敬者。此已十分可识矣。至吾夫子则单提这一个字。以答子路修己之问。又见修己之事。只在此敬。无他别件。而下面安人安百姓。又都在此一个敬也。然而圣学绝讲。但据这一个字而不详其如何用力。于是乎洛闽诸先生之说作焉。盖有以主一无适与整齐严肃言之者矣。有以常惺惺法言之者矣。有以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言之者矣。是无论其有内外偏全地头。只从一处下工。则自该得他在这里。(朱子三方八处皆在其中之譬可见。)而至于所谓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者。则又将这敬。去为此心底骨子。表里始终。都无不贯却。盖至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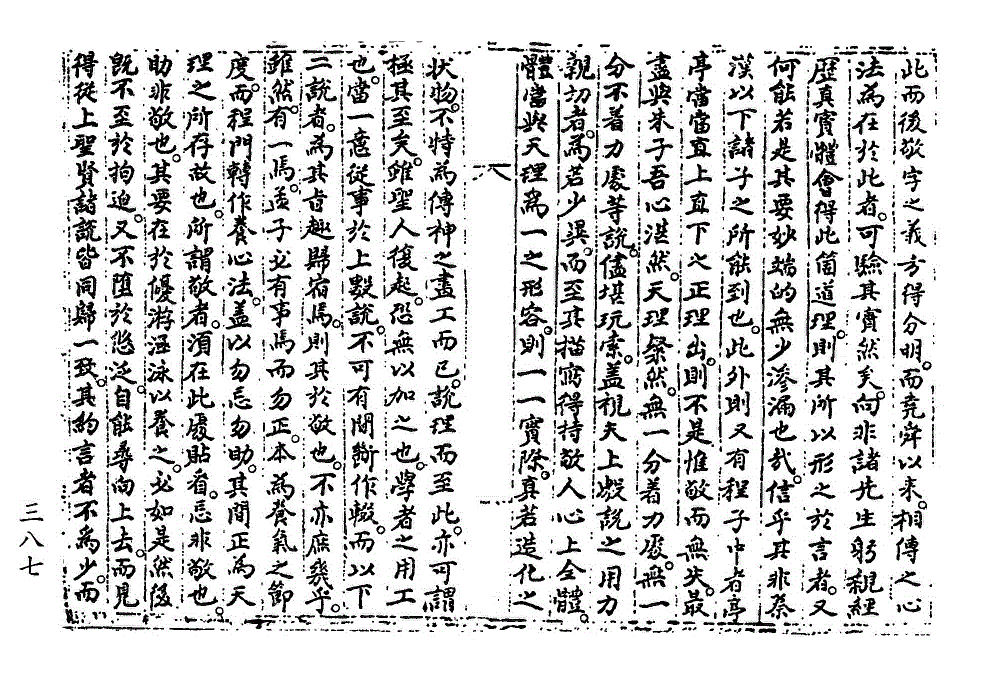 此而后敬字之义方得分明。而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为在于此者。可验其实然矣。向非诸先生躬亲经历真实体会得此个道理。则其所以形之于言者。又何能若是其要妙端的无少渗漏也哉。信乎其非秦汉以下诸子之所能到也。此外则又有程子中者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惟敬而无失。最尽与朱子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无一分不着力处等说。尽堪玩索。盖视夫上数说之用力亲切者。为若少异。而至其描写得持敬人心上全体。体当与天理为一之形容。则一一实际。真若造化之状物。不特为传神之画工而已。说理而至此。亦可谓极其至矣。虽圣人复起。恐无以加之也。学者之用工也。当一意从事于上数说。不可有间断作辍。而以下二说者。为其旨趣归宿焉。则其于敬也。不亦庶几乎。虽然。有一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本为养气之节度。而程门转作养心法。盖以勿忘勿助。其间正为天理之所存故也。所谓敬者。须在此处贴看。忘非敬也。助非敬也。其要在于优游涵泳以养之。必如是然后既不至于拘迫。又不堕于悠泛。自能寻向上去。而见得从上圣贤诸说皆同归一致。其约言者不为少。而
此而后敬字之义方得分明。而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为在于此者。可验其实然矣。向非诸先生躬亲经历真实体会得此个道理。则其所以形之于言者。又何能若是其要妙端的无少渗漏也哉。信乎其非秦汉以下诸子之所能到也。此外则又有程子中者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惟敬而无失。最尽与朱子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无一分不着力处等说。尽堪玩索。盖视夫上数说之用力亲切者。为若少异。而至其描写得持敬人心上全体。体当与天理为一之形容。则一一实际。真若造化之状物。不特为传神之画工而已。说理而至此。亦可谓极其至矣。虽圣人复起。恐无以加之也。学者之用工也。当一意从事于上数说。不可有间断作辍。而以下二说者。为其旨趣归宿焉。则其于敬也。不亦庶几乎。虽然。有一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本为养气之节度。而程门转作养心法。盖以勿忘勿助。其间正为天理之所存故也。所谓敬者。须在此处贴看。忘非敬也。助非敬也。其要在于优游涵泳以养之。必如是然后既不至于拘迫。又不堕于悠泛。自能寻向上去。而见得从上圣贤诸说皆同归一致。其约言者不为少。而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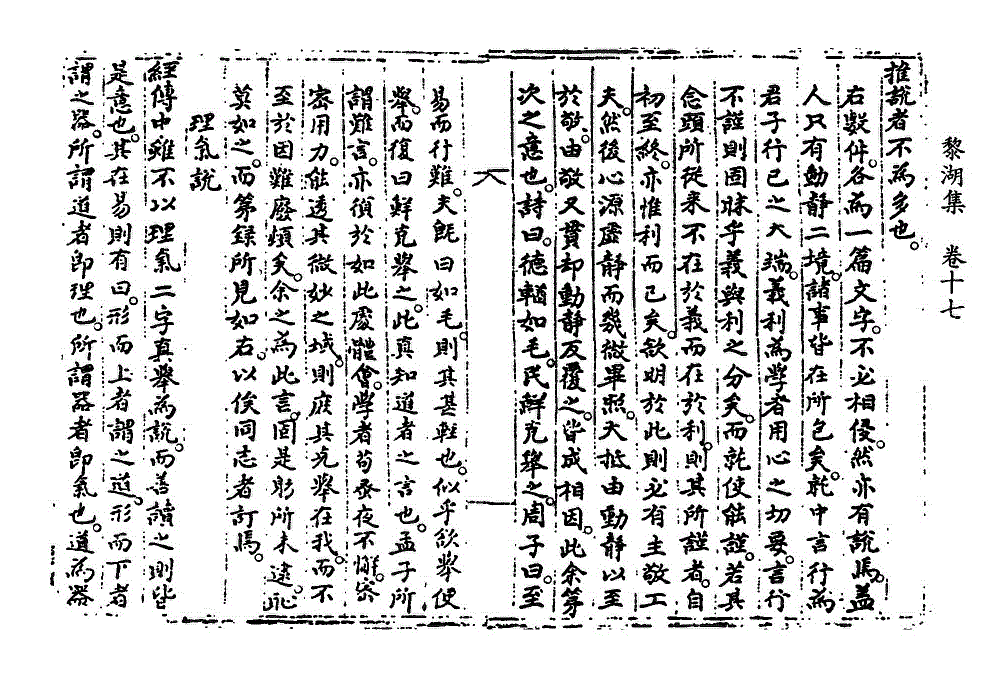 推说者不为多也。
推说者不为多也。右数件。各为一篇文字。不必相侵。然亦有说焉。盖人只有动静二境。诸事皆在所包矣。就中言行为君子行己之大端。义利为学者用心之切要。言行不谨则固昧乎义与利之分矣。而就使能谨。若其念头所从来不在于义而在于利。则其所谨者。自初至终。亦惟利而已矣。欲明于此则必有主敬工夫。然后心源虚静而几微毕照。大抵由动静以至于敬。由敬又贯却动静反覆之。皆成相因。此余第次之意也。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周子曰。至易而行难。夫既曰如毛。则其甚轻也。似乎欲举便举。而复曰鲜克举之。此真知道者之言也。孟子所谓难言。亦须于如此处体会。学者苟蚤夜不懈。密密用力。能透其微妙之域。则庶其克举在我。而不至于因难废顿矣。余之为此言。固是躬所未逮。耻莫如之。而第录所见如右。以俟同志者订焉。
理气说
经传中虽不以理气二字真举为说。而善读之则皆是意也。其在易则有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道者即理也。所谓器者即气也。道为器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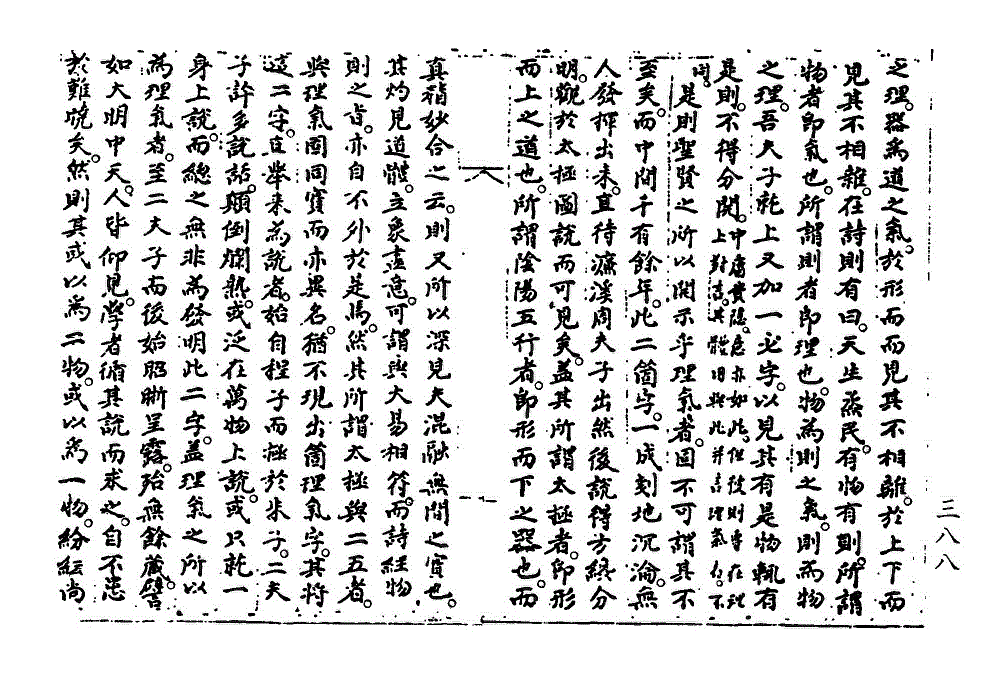 之理。器为道之气。于形而而(而衍字)见其不相离。于上下而见其不相杂。在诗则有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所谓物者即气也。所谓则者即理也。物为则之气。则为物之理。吾夫子就上又加一必字。以见其有是物辄有是则。不得分开。(中庸费隐。意亦如此。但彼则专在理上对言。其体用与此并言理气者。不同。)是则圣贤之所以开示乎理气者。固不可谓其不至矣。而中间千有馀年。此二个字。一成刬地沉沦。无人发挥出来。直待濂溪周夫子出然后说得方才分明。观于太极图说而可见矣。盖其所谓太极者。即形而上之道也。所谓阴阳五行者。即形而下之器也。而真精妙合之云。则又所以深见夫混融无间之实也。其灼见道体。立象尽意。可谓与大易相符。而诗经物则之旨。亦自不外于是焉。然其所谓太极与二五者。与理气固同实而亦异名。犹不现出个理气字。其将这二字。直举来为说者。始自程子而极于朱子。二夫子许多说话。颠倒烂熟。或泛在万物上说。或只就一身上说。而总之无非为发明此二字。盖理气之所以为理气者。至二夫子而后始昭晢呈露。殆无馀藏。譬如大明中天。人皆仰见。学者循其说而求之。自不患于难晓矣。然则其或以为二物。或以为一物。纷纭尚
之理。器为道之气。于形而而(而衍字)见其不相离。于上下而见其不相杂。在诗则有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所谓物者即气也。所谓则者即理也。物为则之气。则为物之理。吾夫子就上又加一必字。以见其有是物辄有是则。不得分开。(中庸费隐。意亦如此。但彼则专在理上对言。其体用与此并言理气者。不同。)是则圣贤之所以开示乎理气者。固不可谓其不至矣。而中间千有馀年。此二个字。一成刬地沉沦。无人发挥出来。直待濂溪周夫子出然后说得方才分明。观于太极图说而可见矣。盖其所谓太极者。即形而上之道也。所谓阴阳五行者。即形而下之器也。而真精妙合之云。则又所以深见夫混融无间之实也。其灼见道体。立象尽意。可谓与大易相符。而诗经物则之旨。亦自不外于是焉。然其所谓太极与二五者。与理气固同实而亦异名。犹不现出个理气字。其将这二字。直举来为说者。始自程子而极于朱子。二夫子许多说话。颠倒烂熟。或泛在万物上说。或只就一身上说。而总之无非为发明此二字。盖理气之所以为理气者。至二夫子而后始昭晢呈露。殆无馀藏。譬如大明中天。人皆仰见。学者循其说而求之。自不患于难晓矣。然则其或以为二物。或以为一物。纷纭尚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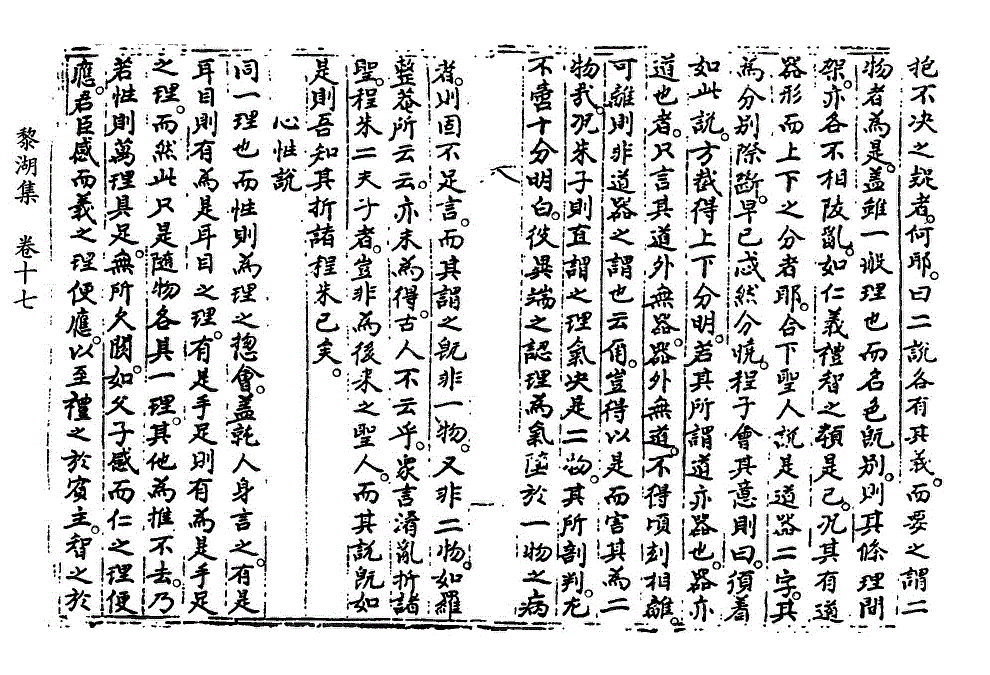 抱不决之疑者。何耶。曰二说各有其义。而要之谓二物者为是。盖虽一般理也而名色既别。则其条理间架。亦各不相陵乱。如仁义礼智之类是已。况其有道器形而上下之分者耶。合下圣人说是道器二字。其为分别际断。早已忒然分晓。程子会其意则曰。须着如此说。方截得上下分明。若其所谓道亦器也。器亦道也者。只言其道外无器。器外无道。不得顷刻相离。可离则非道器之谓也云尔。岂得以是而害其为二物哉。况朱子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其所剖判。尤不啻十分明白。彼异端之认理为气堕于一物之病者。则固不足言。而其谓之既非一物。又非二物。如罗整庵所云云。亦未为得。古人不云乎。众言淆乱折诸圣。程朱二夫子者。岂非为后来之圣人。而其说既如是则吾知其折诸程朱已矣。
抱不决之疑者。何耶。曰二说各有其义。而要之谓二物者为是。盖虽一般理也而名色既别。则其条理间架。亦各不相陵乱。如仁义礼智之类是已。况其有道器形而上下之分者耶。合下圣人说是道器二字。其为分别际断。早已忒然分晓。程子会其意则曰。须着如此说。方截得上下分明。若其所谓道亦器也。器亦道也者。只言其道外无器。器外无道。不得顷刻相离。可离则非道器之谓也云尔。岂得以是而害其为二物哉。况朱子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其所剖判。尤不啻十分明白。彼异端之认理为气堕于一物之病者。则固不足言。而其谓之既非一物。又非二物。如罗整庵所云云。亦未为得。古人不云乎。众言淆乱折诸圣。程朱二夫子者。岂非为后来之圣人。而其说既如是则吾知其折诸程朱已矣。心性说
同一理也而性则为理之揔会。盖就人身言之。有是耳目则有为是耳目之理。有是手足则有为是手足之理。而然此只是随物各具一理。其他为推不去。乃若性则万理具足。无所欠阙。如父子感而仁之理便应。君臣感而义之理便应。以至礼之于宾主。智之于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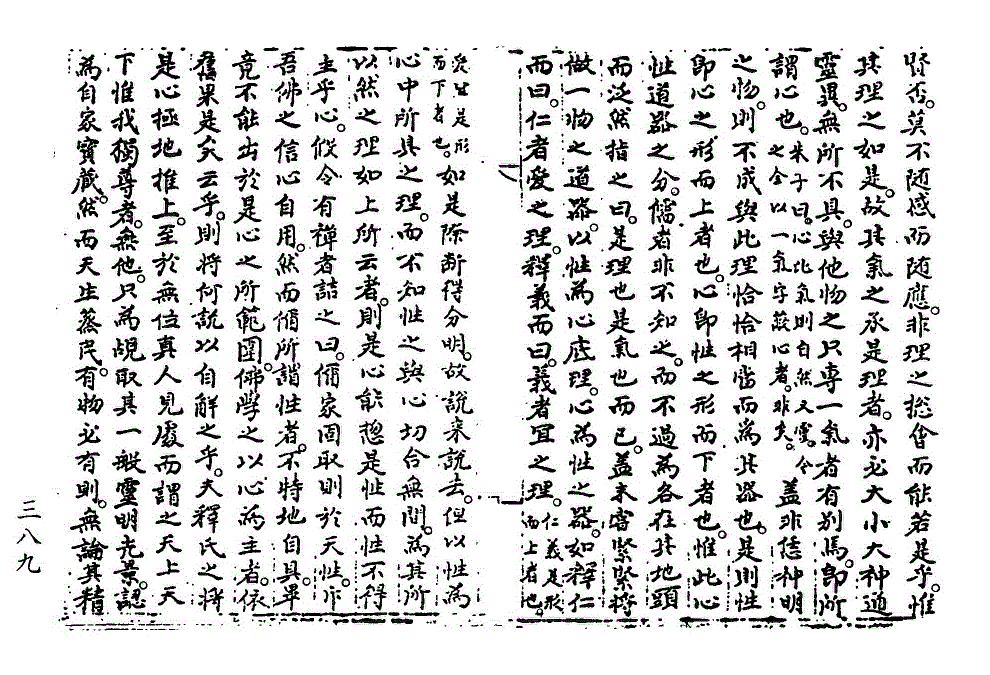 贤否。莫不随感而随应。非理之总会而能若是乎。惟其理之如是。故其气之承是理者。亦必大小大神通灵异。无所不具。与他物之只专一气者有别焉。即所谓心也。(朱子曰。心比气则自然又灵。今之全以一气字蔽心者。非矣。)盖非恁神明之物。则不成与此理恰恰相当而为其器也。是则性即心之形而上者也。心即性之形而下者也。惟此心性道器之分。儒者非不知之。而不过为各在其地头而泛然指之曰。是理也是气也而已。盖未尝紧紧将做一物之道器。以性为心底理。心为性之器。如释仁而曰。仁者爱之理。释义而曰。义者宜之理。(仁义是形而上者也。爱宜是形而下者也。)如是际断得分明。故说来说去。但以性为心中所具之理。而不知性之与心切合无间。为其所以然之理如上所云者。则是心能揔是性而性不得主乎心。假令有禅者诘之曰。你家固取则于天性。斥吾佛之信心自用。然而你所谓性者。不特地自具。毕竟不能出于是心之所范围。佛学之以心为主者。依旧果是矣云乎。则将何说以自解之乎。夫释氏之将是心极地推上。至于无位真人见处而谓之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者。无他。只为觇取其一般灵明光景。认为自家宝藏。然而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则。无论其精
贤否。莫不随感而随应。非理之总会而能若是乎。惟其理之如是。故其气之承是理者。亦必大小大神通灵异。无所不具。与他物之只专一气者有别焉。即所谓心也。(朱子曰。心比气则自然又灵。今之全以一气字蔽心者。非矣。)盖非恁神明之物。则不成与此理恰恰相当而为其器也。是则性即心之形而上者也。心即性之形而下者也。惟此心性道器之分。儒者非不知之。而不过为各在其地头而泛然指之曰。是理也是气也而已。盖未尝紧紧将做一物之道器。以性为心底理。心为性之器。如释仁而曰。仁者爱之理。释义而曰。义者宜之理。(仁义是形而上者也。爱宜是形而下者也。)如是际断得分明。故说来说去。但以性为心中所具之理。而不知性之与心切合无间。为其所以然之理如上所云者。则是心能揔是性而性不得主乎心。假令有禅者诘之曰。你家固取则于天性。斥吾佛之信心自用。然而你所谓性者。不特地自具。毕竟不能出于是心之所范围。佛学之以心为主者。依旧果是矣云乎。则将何说以自解之乎。夫释氏之将是心极地推上。至于无位真人见处而谓之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者。无他。只为觇取其一般灵明光景。认为自家宝藏。然而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则。无论其精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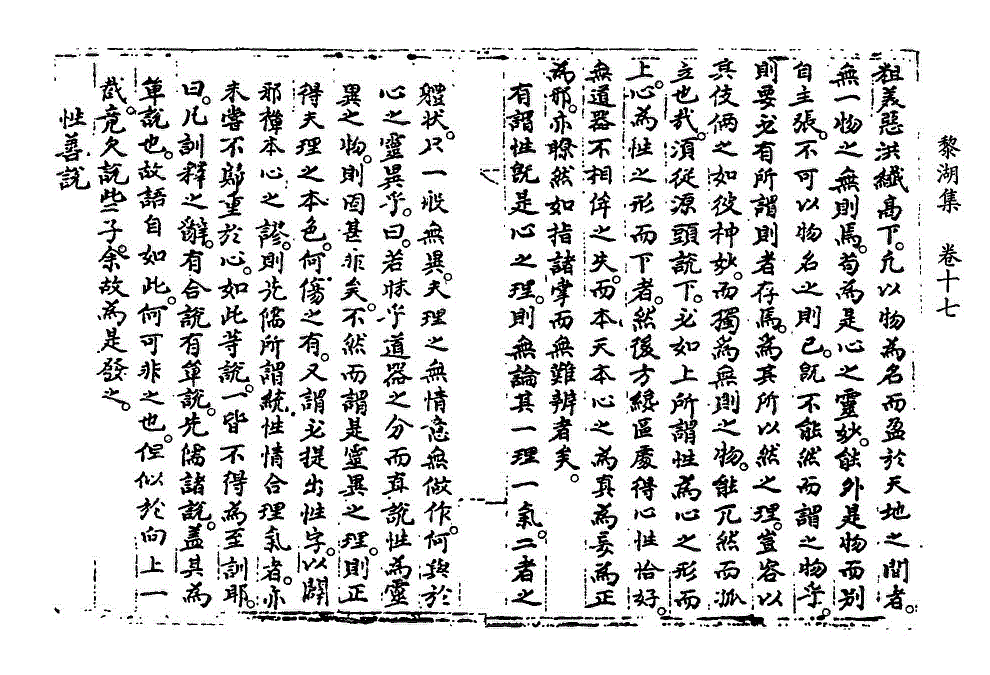 粗美恶洪纤高下。凡以物为名而盈于天地之间者。无一物之无则焉。苟为是心之灵妙。能外是物而别自主张。不可以物名之则已。既不能然而谓之物乎。则要必有所谓则者存焉。为其所以然之理。岂容以其伎俩之如彼神妙。而独为无则之物。能兀然而孤立也哉。须从源头说下。必如上所谓性为心之形而上。心为性之形而下者。然后方才区处得心性恰好。无道器不相侔之失。而本天本心之为真为妄为正为邪。亦瞭然如指诸掌而无难辨者矣。
粗美恶洪纤高下。凡以物为名而盈于天地之间者。无一物之无则焉。苟为是心之灵妙。能外是物而别自主张。不可以物名之则已。既不能然而谓之物乎。则要必有所谓则者存焉。为其所以然之理。岂容以其伎俩之如彼神妙。而独为无则之物。能兀然而孤立也哉。须从源头说下。必如上所谓性为心之形而上。心为性之形而下者。然后方才区处得心性恰好。无道器不相侔之失。而本天本心之为真为妄为正为邪。亦瞭然如指诸掌而无难辨者矣。有谓性既是心之理。则无论其一理一气。二者之体状。只一般无异。夫理之无情意无做作。何与于心之灵异乎。曰。若昧乎道器之分而直说性为灵异之物。则固甚非矣。不然而谓是灵异之理。则正得夫理之本色。何伤之有。又谓必提出性字。以辟邪禅本心之谬。则先儒所谓统性情合理气者。亦未尝不归重于心。如此等说。一皆不得为至训耶。曰。凡训释之辞。有合说有单说。先儒诸说。盖其为单说也。故语自如此。何可非之也。但似于向上一截。竟欠说些子。余故为是发之。
性善说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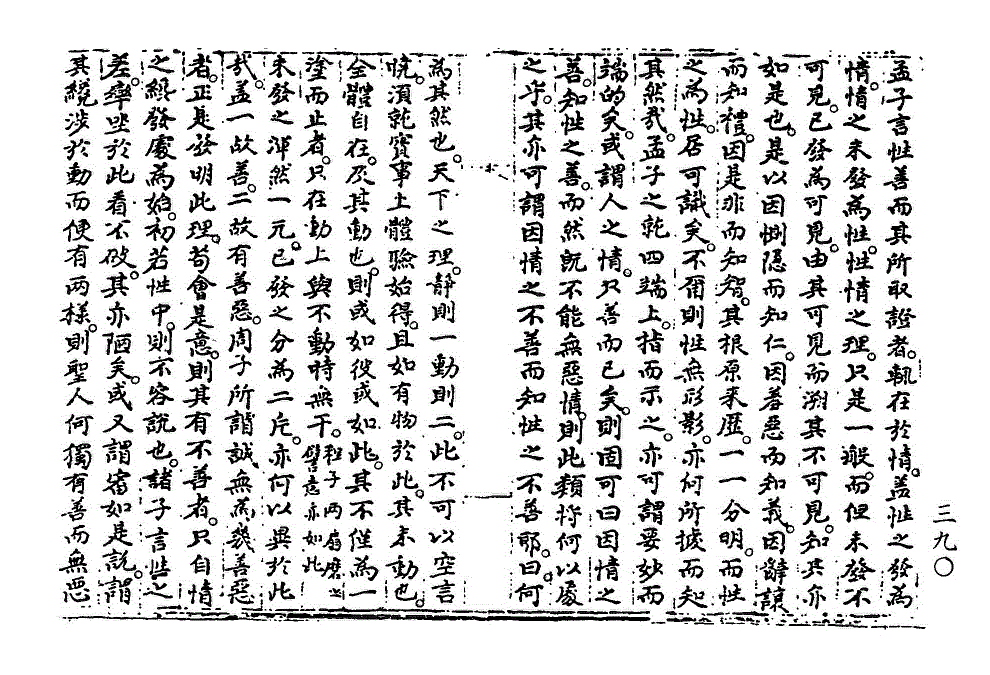 孟子言性善而其所取證者。辄在于情。盖性之发为情。情之未发为性。性情之理。只是一般。而但未发不可见。已发为可见。由其可见而溯其不可见。知其亦如是也。是以因恻隐而知仁。因羞恶而知义。因辞让而知礼。因是非而知智。其根原来历。一一分明。而性之为性。居可识矣。不尔则性无形影。亦何所据而知其然哉。孟子之就四端上。指而示之。亦可谓要妙而端的矣。或谓人之情。只善而已矣。则固可曰因情之善。知性之善。而然既不能无恶情。则此类将何以处之乎。其亦可谓因情之不善而知性之不善耶。曰。何为其然也。天下之理。静则一动则二。此不可以空言晓。须就实事上体验始得。且如有物于此。其未动也。全体自在。及其动也。则或如彼或如此。其不仅为一涂而止者。只在动上与不动时无干。(程子两扇磨之譬意亦如此。)未发之浑然一元。已发之分为二片。亦何以异于此哉。盖一故善。二故有善恶。周子所谓诚无为几善恶者。正是发明此理。苟会是意。则其有不善者。只自情之才发处为始。初若性中。则不容说也。诸子言性之差。率坐于此看不破。其亦陋矣。或又谓审如是说。谓其才涉于动而便有两样。则圣人何独有善而无恶
孟子言性善而其所取證者。辄在于情。盖性之发为情。情之未发为性。性情之理。只是一般。而但未发不可见。已发为可见。由其可见而溯其不可见。知其亦如是也。是以因恻隐而知仁。因羞恶而知义。因辞让而知礼。因是非而知智。其根原来历。一一分明。而性之为性。居可识矣。不尔则性无形影。亦何所据而知其然哉。孟子之就四端上。指而示之。亦可谓要妙而端的矣。或谓人之情。只善而已矣。则固可曰因情之善。知性之善。而然既不能无恶情。则此类将何以处之乎。其亦可谓因情之不善而知性之不善耶。曰。何为其然也。天下之理。静则一动则二。此不可以空言晓。须就实事上体验始得。且如有物于此。其未动也。全体自在。及其动也。则或如彼或如此。其不仅为一涂而止者。只在动上与不动时无干。(程子两扇磨之譬意亦如此。)未发之浑然一元。已发之分为二片。亦何以异于此哉。盖一故善。二故有善恶。周子所谓诚无为几善恶者。正是发明此理。苟会是意。则其有不善者。只自情之才发处为始。初若性中。则不容说也。诸子言性之差。率坐于此看不破。其亦陋矣。或又谓审如是说。谓其才涉于动而便有两样。则圣人何独有善而无恶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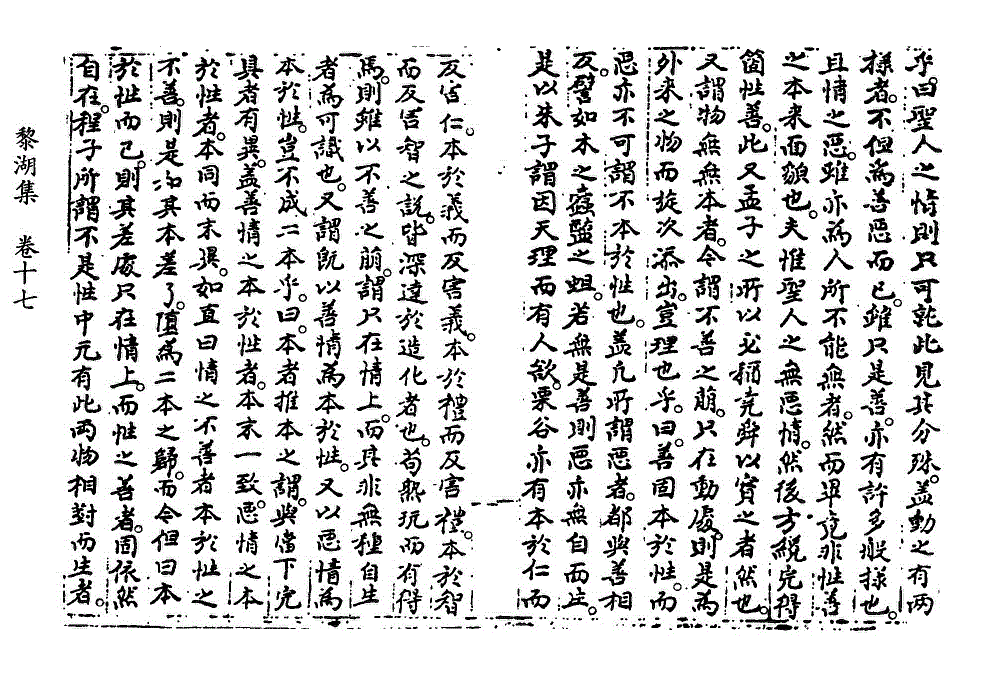 乎。曰圣人之情则只可就此见其分殊。盖动之有两样者。不但为善恶而已。虽只是善。亦有许多般㨾也。且情之恶。虽亦为人所不能无者。然而毕竟非性善之本来面貌也。夫惟圣人之无恶情。然后方才完得个性善。此又孟子之所以必称尧舜以实之者然也。又谓物无无本者。今谓不善之萌。只在动处。则是为外来之物而旋次添出。岂理也乎。曰。善固本于性。而恶亦不可谓不本于性也。盖凡所谓恶者。都与善相反。譬如木之蠹盐之蛆。若无是善则恶亦无自而生。是以朱子谓因天理而有人欲。栗谷亦有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礼。本于智而反害智之说。皆深达于造化者也。苟熟玩而有得焉。则虽以不善之萌。谓只在情上。而其非无种自生者为可识也。又谓既以善情为本于性。又以恶情为本于性。岂不成二本乎。曰。本者推本之谓。与当下完具者有异。盖善情之本于性者。本末一致。恶情之本于性者。本同而末异。如直曰情之不善者本于性之不善。则是知其本差了。堕为二本之归。而今但曰本于性而已。则其差处只在情上。而性之善者。固依然自在。程子所谓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者。
乎。曰圣人之情则只可就此见其分殊。盖动之有两样者。不但为善恶而已。虽只是善。亦有许多般㨾也。且情之恶。虽亦为人所不能无者。然而毕竟非性善之本来面貌也。夫惟圣人之无恶情。然后方才完得个性善。此又孟子之所以必称尧舜以实之者然也。又谓物无无本者。今谓不善之萌。只在动处。则是为外来之物而旋次添出。岂理也乎。曰。善固本于性。而恶亦不可谓不本于性也。盖凡所谓恶者。都与善相反。譬如木之蠹盐之蛆。若无是善则恶亦无自而生。是以朱子谓因天理而有人欲。栗谷亦有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礼。本于智而反害智之说。皆深达于造化者也。苟熟玩而有得焉。则虽以不善之萌。谓只在情上。而其非无种自生者为可识也。又谓既以善情为本于性。又以恶情为本于性。岂不成二本乎。曰。本者推本之谓。与当下完具者有异。盖善情之本于性者。本末一致。恶情之本于性者。本同而末异。如直曰情之不善者本于性之不善。则是知其本差了。堕为二本之归。而今但曰本于性而已。则其差处只在情上。而性之善者。固依然自在。程子所谓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者。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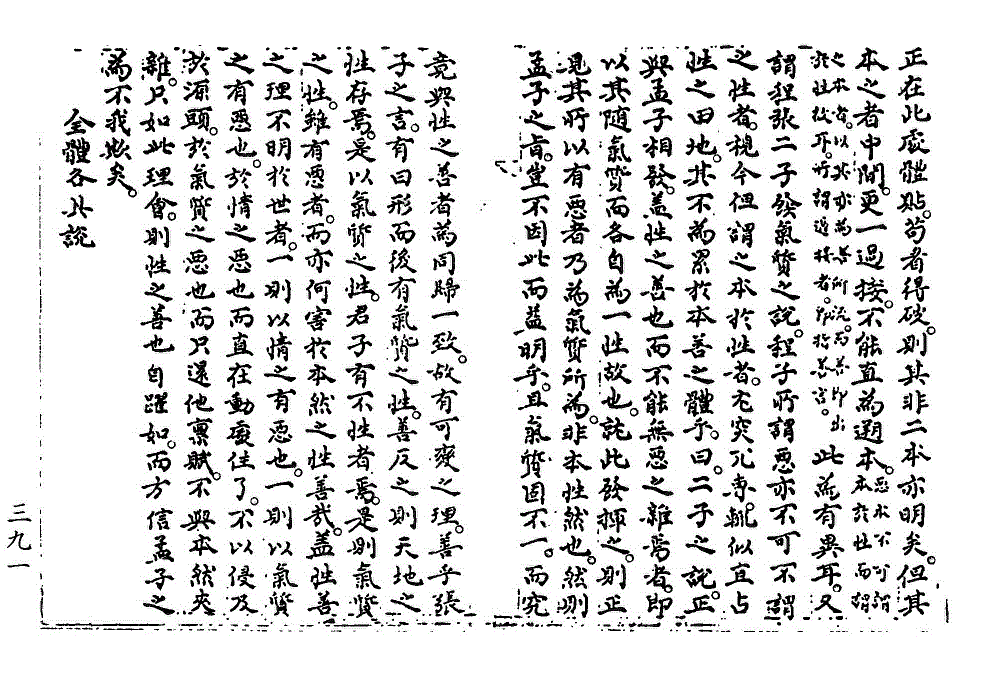 正在此处体贴。苟看得破。则其非二本亦明矣。但其本之者中间。更一过接。不能直为溯本。(恶本不可谓本于性而谓之本者。以其亦为善所流。而善即出于性故耳。所谓过接者。即指善言。)此为有异耳。又谓程张二子发气质之说。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者。视今但谓之本于性者。尤突兀专。辄似宜占性之田地。其不为累于本善之体乎。曰。二子之说。正与孟子相发。盖性之善也而不能无恶之杂焉者。即以其随气质而各自为一性故也。就此发挥之。则正见其所以有恶者乃为气质所为。非本性然也。然则孟子之旨。岂不因此而益明乎。且气质固不一。而究竟与性之善者为同归一致。故有可变之理。善乎张子之言。有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是以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是则气质之性。虽有恶者。而亦何害于本然之性善哉。盖性善之理不明于世者。一则以情之有恶也。一则以气质之有恶也。于情之恶也而直在动处住了。不以侵及于源头。于气质之恶也而只还他禀赋。不与本然夹杂。只如此理会。则性之善也自跃如。而方信孟子之为不我欺矣。
正在此处体贴。苟看得破。则其非二本亦明矣。但其本之者中间。更一过接。不能直为溯本。(恶本不可谓本于性而谓之本者。以其亦为善所流。而善即出于性故耳。所谓过接者。即指善言。)此为有异耳。又谓程张二子发气质之说。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者。视今但谓之本于性者。尤突兀专。辄似宜占性之田地。其不为累于本善之体乎。曰。二子之说。正与孟子相发。盖性之善也而不能无恶之杂焉者。即以其随气质而各自为一性故也。就此发挥之。则正见其所以有恶者乃为气质所为。非本性然也。然则孟子之旨。岂不因此而益明乎。且气质固不一。而究竟与性之善者为同归一致。故有可变之理。善乎张子之言。有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是以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是则气质之性。虽有恶者。而亦何害于本然之性善哉。盖性善之理不明于世者。一则以情之有恶也。一则以气质之有恶也。于情之恶也而直在动处住了。不以侵及于源头。于气质之恶也而只还他禀赋。不与本然夹杂。只如此理会。则性之善也自跃如。而方信孟子之为不我欺矣。全体各具说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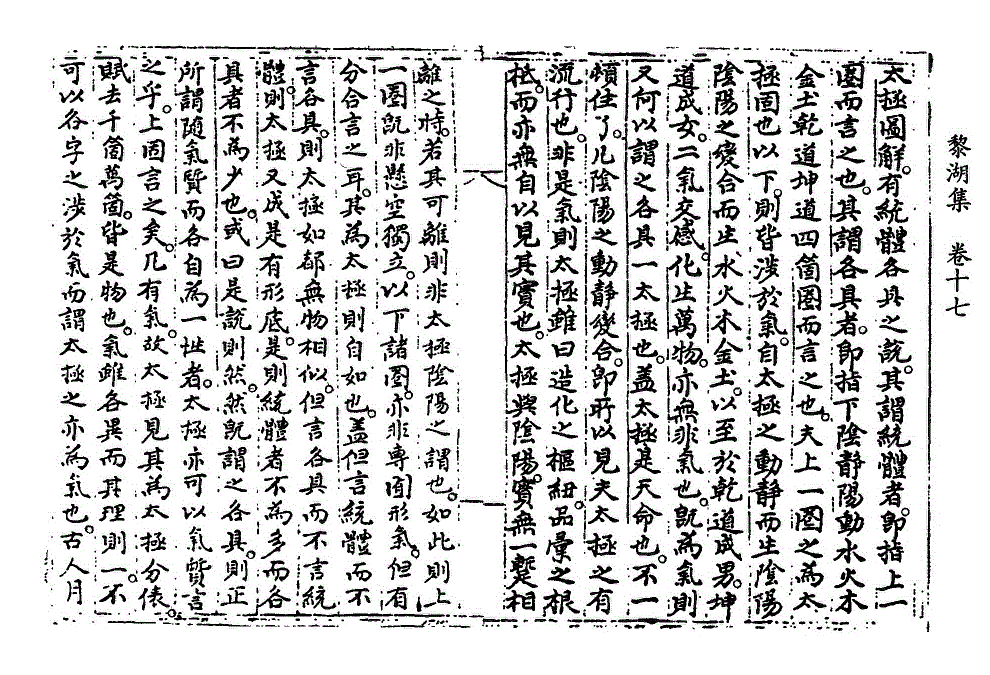 太极图解。有统体各具之说。其谓统体者。即指上一圈而言之也。其谓各具者。即指下阴静阳动水火木金土乾道坤道四个圈而言之也。夫上一圈之为太极固也以下。则皆涉于气。自太极之动静而生阴阳阴阳之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以至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亦无非气也。既为气则又何以谓之各具一太极也。盖太极是天命也。不一顿住了。凡阴阳之动静变合。即所以见夫太极之有流行也。非是气则太极虽曰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而亦无自以见其实也。太极与阴阳。实无一暂相离之时。若其可离则非太极阴阳之谓也。如此则上一圈既非悬空独立。以下诸圈。亦非专囿形气。但有分合言之耳。其为太极则自如也。盖但言统体而不言各具。则太极如都无物相似。但言各具而不言统体。则太极又成是有形底。是则统体者不为多而各具者不为少也。或曰是说则然。然既谓之各具。则正所谓随气质而各自为一性者。太极亦可以气质言之乎。上固言之矣。凡有气。故太极见其为太极分俵。赋去千个万个。皆是物也。气虽各异而其理则一。不可以各字之涉于气而谓太极之亦为气也。古人月
太极图解。有统体各具之说。其谓统体者。即指上一圈而言之也。其谓各具者。即指下阴静阳动水火木金土乾道坤道四个圈而言之也。夫上一圈之为太极固也以下。则皆涉于气。自太极之动静而生阴阳阴阳之变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以至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亦无非气也。既为气则又何以谓之各具一太极也。盖太极是天命也。不一顿住了。凡阴阳之动静变合。即所以见夫太极之有流行也。非是气则太极虽曰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而亦无自以见其实也。太极与阴阳。实无一暂相离之时。若其可离则非太极阴阳之谓也。如此则上一圈既非悬空独立。以下诸圈。亦非专囿形气。但有分合言之耳。其为太极则自如也。盖但言统体而不言各具。则太极如都无物相似。但言各具而不言统体。则太极又成是有形底。是则统体者不为多而各具者不为少也。或曰是说则然。然既谓之各具。则正所谓随气质而各自为一性者。太极亦可以气质言之乎。上固言之矣。凡有气。故太极见其为太极分俵。赋去千个万个。皆是物也。气虽各异而其理则一。不可以各字之涉于气而谓太极之亦为气也。古人月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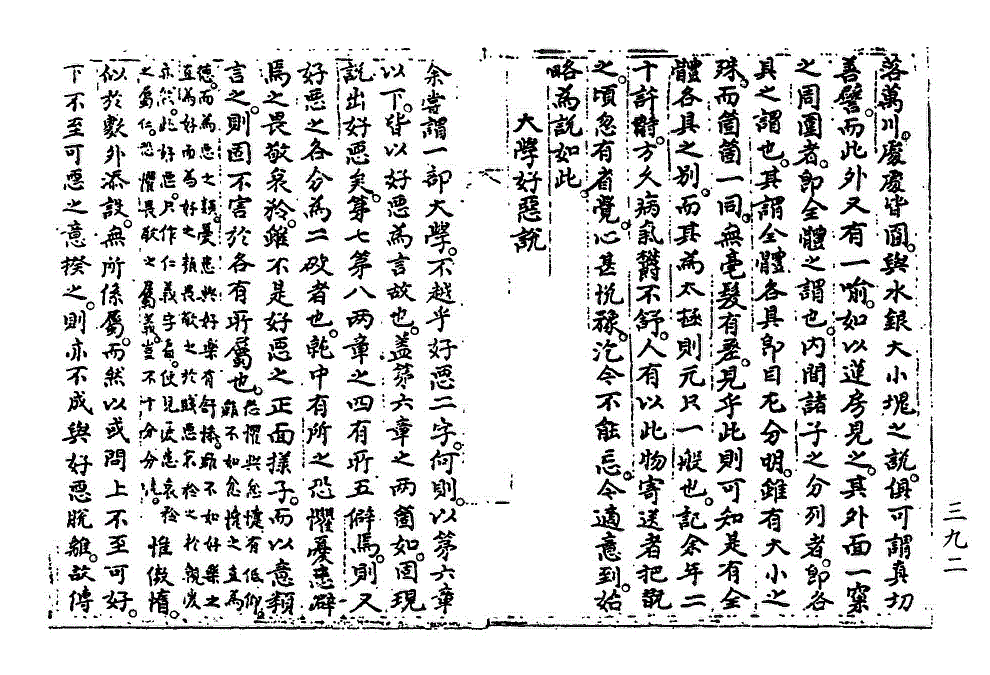 落万川。处处皆囿。与水银大小块之说。俱可谓真切善譬。而此外又有一喻。如以莲房见之。其外面一窠之周围者。即全体之谓也。内间诸子之分列者。即各具之谓也。其谓全体各具即目尤分明。虽有大小之殊。而个个一同。无毫发有差。见乎此则可知是有全体各具之别。而其为太极则元只一般也。记余年二十许时。方久病气郁不舒。人有以此物寄送者把玩之。顷忽有省觉。心甚悦豫。汔今不能忘。今适意到。始略为说如此。
落万川。处处皆囿。与水银大小块之说。俱可谓真切善譬。而此外又有一喻。如以莲房见之。其外面一窠之周围者。即全体之谓也。内间诸子之分列者。即各具之谓也。其谓全体各具即目尤分明。虽有大小之殊。而个个一同。无毫发有差。见乎此则可知是有全体各具之别。而其为太极则元只一般也。记余年二十许时。方久病气郁不舒。人有以此物寄送者把玩之。顷忽有省觉。心甚悦豫。汔今不能忘。今适意到。始略为说如此。大学好恶说
余尝谓一部大学。不越乎好恶二字。何则。以第六章以下。皆以好恶为言故也。盖第六章之两个如。固现说出好恶矣。第七第八两章之四有所五僻焉。则又好恶之各分为二破者也。就中有所之恐惧忧患辟焉之畏敬哀矜。虽不是好恶之正面㨾子。而以意类言之。则固不害于各有所属也。(恐惧与忿懥有低仰。虽不如忿懥之直为德。而为恶之类。忧患与好乐有舒惨。虽不如好乐之直为好而为好之类畏敬之于贱恶哀矜之于亲爱亦然。此好恶。只作仁义字看。便见忧患哀矜之属仁。恐惧畏敬之属义。岂不十分分晓。)惟傲惰。似于数外添设。无所系属。而然以或问上不至可好。下不至可恶之意揆之。则亦不成与好恶脱离。故传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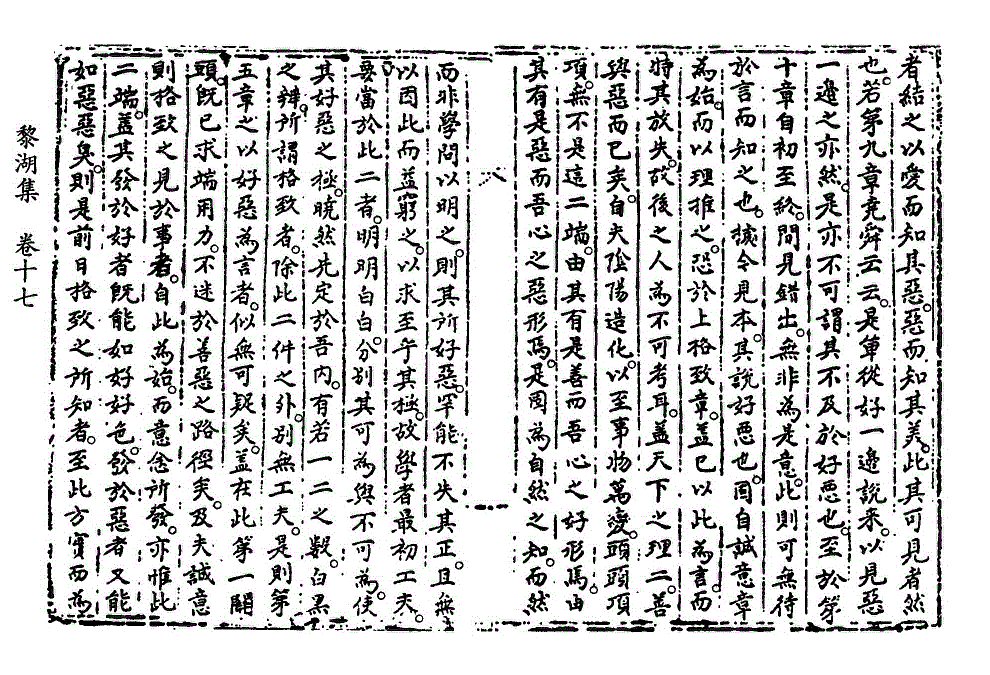 者结之以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此其可见者然也。若第九章尧舜云云。是单从好一边说来。以见恶一边之亦然。是亦不可谓其不及于好恶也。至于第十章自初至终。间见错出。无非为是意。此则可无待于言而知之也。据今见本。其说好恶也。固自诚意章为始。而以理推之。恐于上格致章。盖已以此为言。而特其放失。故后之人为不可考耳。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自夫阴阳造化。以至事物万变。头头项项。无不是这二端。由其有是善而吾心之好形焉。由其有是恶而吾心之恶形焉。是固为自然之知。而然而非学问以明之。则其所好恶。罕能不失其正。且无以因此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故学者最初工夫。要当于此二者。明明白白。分别其可为与不可为。使其好恶之极。晓然先定于吾内。有若一二之数。白黑之辨。所谓格致者。除此二件之外。别无工夫。是则第五章之以好恶为言者。似无可疑矣。盖在此第一关头。既已求端用力。不迷于善恶之路径矣。及夫诚意则格致之见于事者。自此为始。而意念所发。亦惟此二端。盖其发于好者既能如好好色。发于恶者又能如恶恶臭。则是前日格致之所知者。至此方实而为
者结之以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此其可见者然也。若第九章尧舜云云。是单从好一边说来。以见恶一边之亦然。是亦不可谓其不及于好恶也。至于第十章自初至终。间见错出。无非为是意。此则可无待于言而知之也。据今见本。其说好恶也。固自诚意章为始。而以理推之。恐于上格致章。盖已以此为言。而特其放失。故后之人为不可考耳。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自夫阴阳造化。以至事物万变。头头项项。无不是这二端。由其有是善而吾心之好形焉。由其有是恶而吾心之恶形焉。是固为自然之知。而然而非学问以明之。则其所好恶。罕能不失其正。且无以因此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故学者最初工夫。要当于此二者。明明白白。分别其可为与不可为。使其好恶之极。晓然先定于吾内。有若一二之数。白黑之辨。所谓格致者。除此二件之外。别无工夫。是则第五章之以好恶为言者。似无可疑矣。盖在此第一关头。既已求端用力。不迷于善恶之路径矣。及夫诚意则格致之见于事者。自此为始。而意念所发。亦惟此二端。盖其发于好者既能如好好色。发于恶者又能如恶恶臭。则是前日格致之所知者。至此方实而为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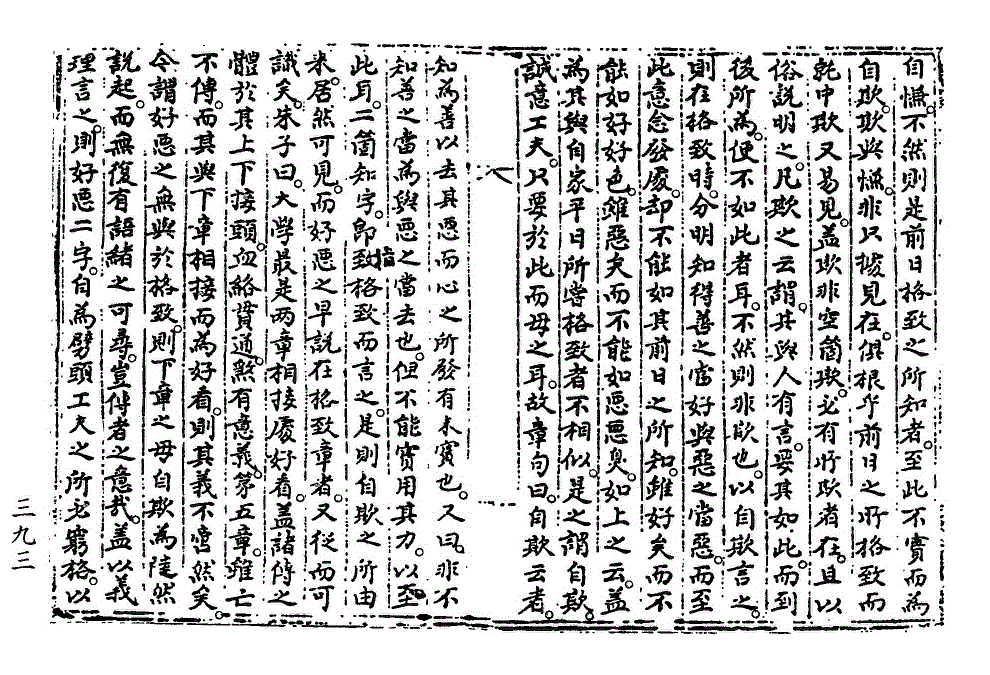 自慊。不然则是前日格致之所知者。至此不实而为自欺。欺与慊。非只据见在。俱根乎前日之所格致而就中欺又易见。盖欺非空个欺。必有所欺者在。且以俗说明之。凡欺之云谓。其与人有言。要其如此。而到后所为。便不如此者耳。不然则非欺也。以自欺言之。则在格致时。分明知得善之当好与恶之当恶。而至此意念发处。却不能如其前日之所知。虽好矣而不能如好好色。虽恶矣而不能如恶恶臭。如上之云。盖为其与自家平日所尝格致者不相似。是之谓自欺。诚意工夫。只要于此而毋之耳。故章句曰。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其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又曰。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二个知字。即致(一作指)格致而言之。是则自欺之所由来。居然可见。而好恶之早说在格致章者。又从而可识矣。朱子曰。大学最是两章相接处好看。盖诸传之体于其上下接头。血络贯通。煞有意义。第五章。虽亡不传。而其与下章相接而为好看。则其义不啻然矣。今谓好恶之无与于格致。则下章之毋自欺为陡然说起。而无复有语绪之可寻。岂传者之意哉。盖以义理言之。则好恶二字。自为劈头工夫之所必穷格。以
自慊。不然则是前日格致之所知者。至此不实而为自欺。欺与慊。非只据见在。俱根乎前日之所格致而就中欺又易见。盖欺非空个欺。必有所欺者在。且以俗说明之。凡欺之云谓。其与人有言。要其如此。而到后所为。便不如此者耳。不然则非欺也。以自欺言之。则在格致时。分明知得善之当好与恶之当恶。而至此意念发处。却不能如其前日之所知。虽好矣而不能如好好色。虽恶矣而不能如恶恶臭。如上之云。盖为其与自家平日所尝格致者不相似。是之谓自欺。诚意工夫。只要于此而毋之耳。故章句曰。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其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又曰。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二个知字。即致(一作指)格致而言之。是则自欺之所由来。居然可见。而好恶之早说在格致章者。又从而可识矣。朱子曰。大学最是两章相接处好看。盖诸传之体于其上下接头。血络贯通。煞有意义。第五章。虽亡不传。而其与下章相接而为好看。则其义不啻然矣。今谓好恶之无与于格致。则下章之毋自欺为陡然说起。而无复有语绪之可寻。岂传者之意哉。盖以义理言之。则好恶二字。自为劈头工夫之所必穷格。以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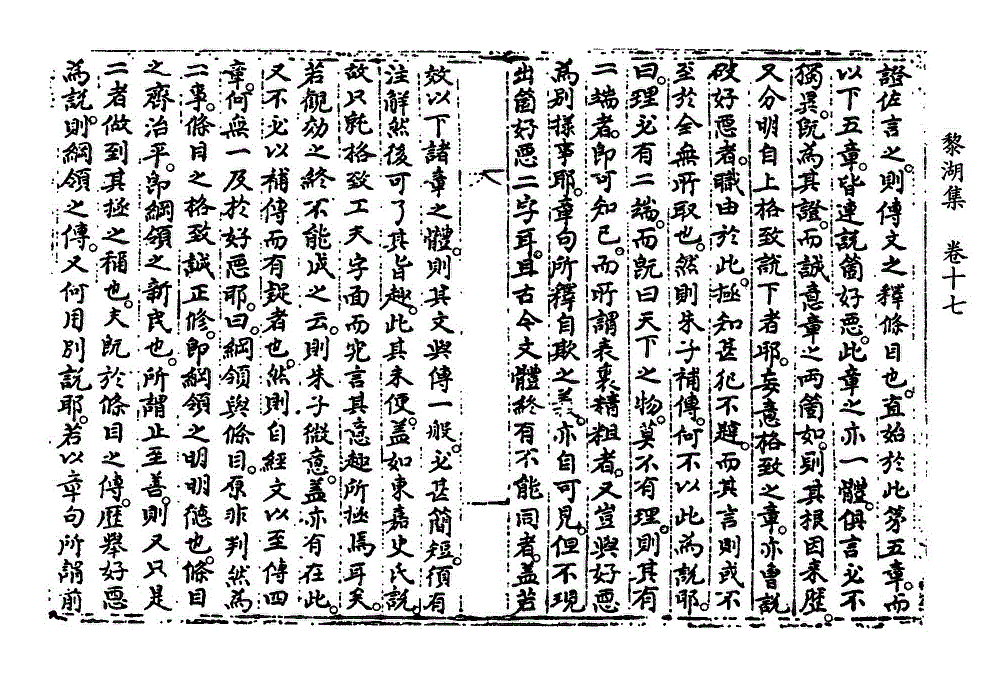 證佐言之。则传文之释条目也。直始于此第五章。而以下五章。皆连说个好恶。此章之亦一体。俱言必不独异。既为其證。而诚意章之两个如。则其根因来历。又分明自上格致说下者耶。妄意格致之章。亦曾说破好恶者。职由于此。极知甚犯不韪。而其言则或不至于全无所取也。然则朱子补传。何不以此为说耶。曰。理必有二端。而既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则其有二端者。即可知已。而所谓表里精粗者。又岂与好恶为别㨾事耶。章句所释自欺之义。亦自可见。但不现出个好恶二字耳。且古今文体终有不能同者。盖若效以下诸章之体。则其文与传一般。必甚简短。须有注解然后可了其旨趣。此其未便。盖如东嘉史氏说。故只就格致工夫字面而究言其意趣所极焉耳矣。若观效之终不能成之云。则朱子微意。盖亦有在此。又不必以补传而有疑者也。然则自经文以至传四章。何无一及于好恶耶。曰。纲领与条目。原非判然为二事。条目之格致诚正修。即纲领之明明德也。条目之齐治平。即纲领之新民也。所谓止至善。则又只是二者做到其极之称也。夫既于条目之传。历举好恶为说。则纲领之传。又何用别说耶。若以章句所谓前
證佐言之。则传文之释条目也。直始于此第五章。而以下五章。皆连说个好恶。此章之亦一体。俱言必不独异。既为其證。而诚意章之两个如。则其根因来历。又分明自上格致说下者耶。妄意格致之章。亦曾说破好恶者。职由于此。极知甚犯不韪。而其言则或不至于全无所取也。然则朱子补传。何不以此为说耶。曰。理必有二端。而既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则其有二端者。即可知已。而所谓表里精粗者。又岂与好恶为别㨾事耶。章句所释自欺之义。亦自可见。但不现出个好恶二字耳。且古今文体终有不能同者。盖若效以下诸章之体。则其文与传一般。必甚简短。须有注解然后可了其旨趣。此其未便。盖如东嘉史氏说。故只就格致工夫字面而究言其意趣所极焉耳矣。若观效之终不能成之云。则朱子微意。盖亦有在此。又不必以补传而有疑者也。然则自经文以至传四章。何无一及于好恶耶。曰。纲领与条目。原非判然为二事。条目之格致诚正修。即纲领之明明德也。条目之齐治平。即纲领之新民也。所谓止至善。则又只是二者做到其极之称也。夫既于条目之传。历举好恶为说。则纲领之传。又何用别说耶。若以章句所谓前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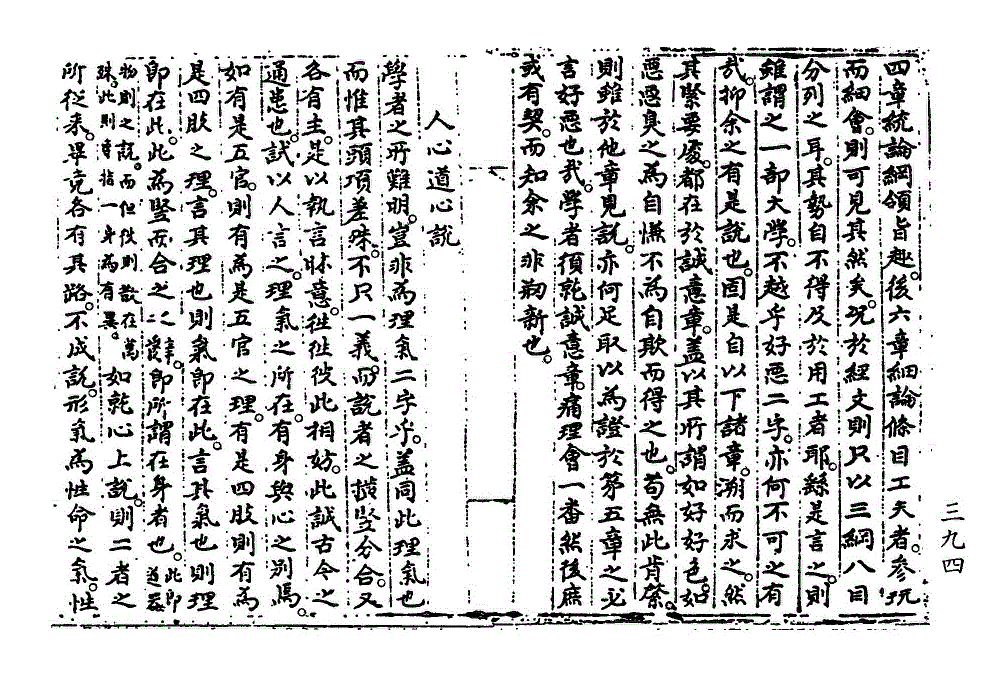 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者。参玩而细会。则可见其然矣。况于经文则只以三纲八目分列之耳。其势自不得及于用工者耶。繇是言之。则虽谓之一部大学。不越乎好恶二字。亦何不可之有哉。抑余之有是说也。固是自以下诸章。溯而求之。然其紧要处。都在于诚意章。盖以其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为自慊不为自欺而得之也。苟无此肯綮。则虽于他章见说。亦何足取以为證于第五章之必言好恶也哉。学者须就诚意章。痛理会一番然后庶或有契。而知余之非刱新也。
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者。参玩而细会。则可见其然矣。况于经文则只以三纲八目分列之耳。其势自不得及于用工者耶。繇是言之。则虽谓之一部大学。不越乎好恶二字。亦何不可之有哉。抑余之有是说也。固是自以下诸章。溯而求之。然其紧要处。都在于诚意章。盖以其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为自慊不为自欺而得之也。苟无此肯綮。则虽于他章见说。亦何足取以为證于第五章之必言好恶也哉。学者须就诚意章。痛理会一番然后庶或有契。而知余之非刱新也。人心道心说
学者之所难明。岂非为理气二字乎。盖同此理气也而惟其头项差殊。不只一义。而说者之横竖分合。又各有主。是以执言昧意。往往彼此相妨。此诚古今之通患也。试以人言之。理气之所在。有身与心之别焉。如有是五官。则有为是五官之理。有是四肢则有为是四肢之理。言其理也则气即在此。言其气也则理即在此。此为竖而合之之辞。即所谓在身者也。(此即道器物则之说。而但彼则散在万殊。此则专指一身为有异。)如就心上说。则二者之所从来。毕竟各有其路。不成说。形气为性命之气。性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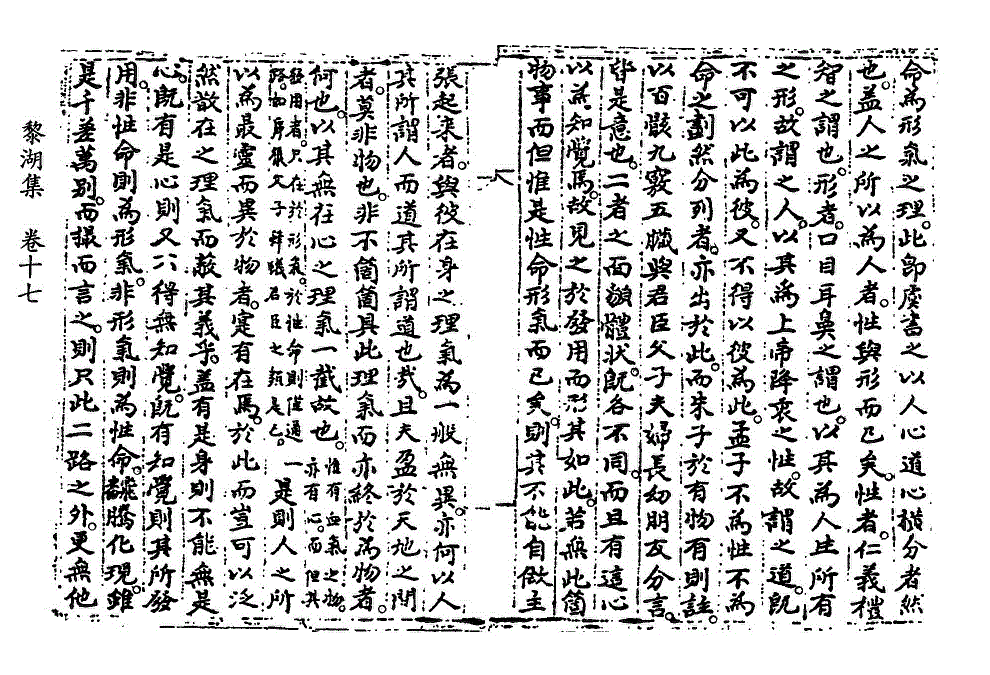 命为形气之理。此即虞书之以人心道心横分者然也。盖人之所以为人者。性与形而已矣。性者。仁义礼智之谓也。形者。口目耳鼻之谓也。以其为人生所有之形。故谓之人。以其为上帝降衷之性。故谓之道。既不可以此为彼。又不得以彼为此。孟子不为性不为命之划然分列者。亦出于此。而朱子于有物有则注。以百骸九窍五脏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分言。皆是意也。二者之面貌体状。既各不同。而且有这心以为知觉焉。故见之于发用而形其如此。若无此个物事而但惟是性命形气而已矣。则其不能自做主张起来者。与彼在身之理气为一般无异。亦何以人其所谓人而道其所谓道也哉。且夫盈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也。非不个个具此理气而亦终于为物者。何也。以其无在心之理气一截故也。(惟有血气之物。亦有心。而但其发用者。只在于形气。于性命则仅通一路。如虎狼父子蜂蚁君臣之类是已。)是则人之所以为最灵而异于物者。寔有在焉。于此而岂可以泛然散在之理气而蔽其义乎。盖有是身则不能无是心。既有是心则又不得无知觉。既有知觉则其所发用。非性命则为形气。非形气则为性命。翻腾化现。虽是千差万别。而撮而言之。则只此二路之外。更无他
命为形气之理。此即虞书之以人心道心横分者然也。盖人之所以为人者。性与形而已矣。性者。仁义礼智之谓也。形者。口目耳鼻之谓也。以其为人生所有之形。故谓之人。以其为上帝降衷之性。故谓之道。既不可以此为彼。又不得以彼为此。孟子不为性不为命之划然分列者。亦出于此。而朱子于有物有则注。以百骸九窍五脏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分言。皆是意也。二者之面貌体状。既各不同。而且有这心以为知觉焉。故见之于发用而形其如此。若无此个物事而但惟是性命形气而已矣。则其不能自做主张起来者。与彼在身之理气为一般无异。亦何以人其所谓人而道其所谓道也哉。且夫盈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也。非不个个具此理气而亦终于为物者。何也。以其无在心之理气一截故也。(惟有血气之物。亦有心。而但其发用者。只在于形气。于性命则仅通一路。如虎狼父子蜂蚁君臣之类是已。)是则人之所以为最灵而异于物者。寔有在焉。于此而岂可以泛然散在之理气而蔽其义乎。盖有是身则不能无是心。既有是心则又不得无知觉。既有知觉则其所发用。非性命则为形气。非形气则为性命。翻腾化现。虽是千差万别。而撮而言之。则只此二路之外。更无他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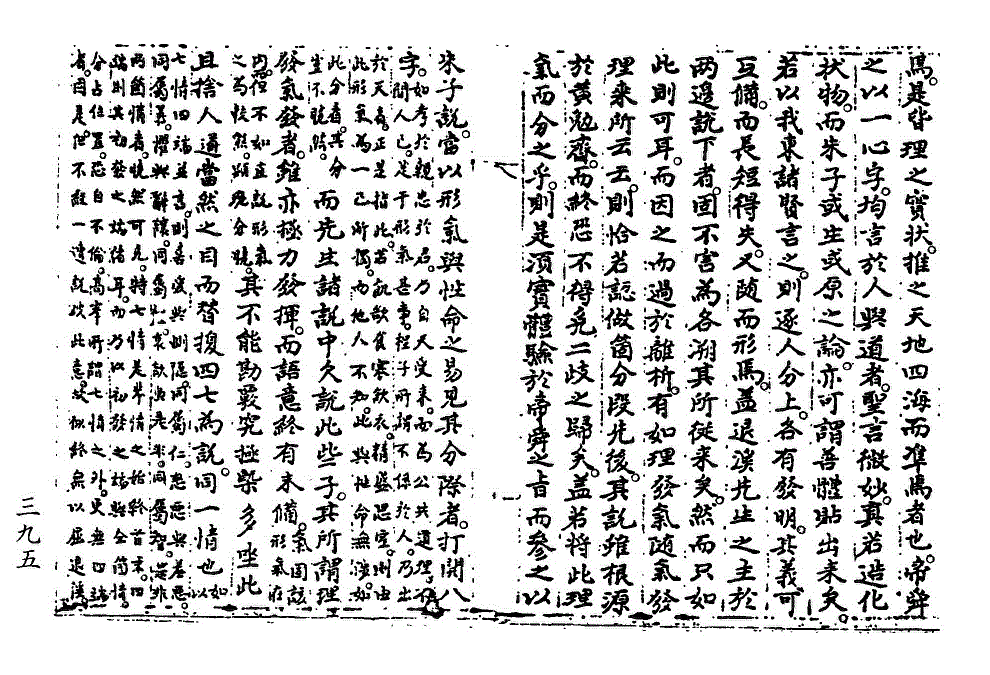 焉。是皆理之实状。推之天地四海而准焉者也。帝舜之以一心字。均言于人与道者。圣言微妙。真若造化状物。而朱子或生或原之论。亦可谓善体贴出来矣。若以我东诸贤言之。则逐人分上。各有发明。其义可互备。而长短得失。又随而形焉。盖退溪先生之主于两边说下者。固不害为各溯其所从来矣。然而只如此则可耳。而因之而过于离析。有如理发气随气发理来所云云。则恰若认做个分段先后。其说虽根源于黄勉斋。而终恐不得免二歧之归矣。盖若将此理气而分之乎。则是须实体验于帝舜之旨而参之以朱子说。当以形气与性命之易见其分际者。打开八字。(如孝于亲忠于君。乃自天受来。而为公共道理。不问人己。是于形气甚事。程子所谓不系于人。乃出于天者。正是指此。若饥欲食寒欲衣。精盛思室。则由此形气为一己所独。而他人不知。此与性命无涉。如此分看。其分岂不晓然。)而先生诸说中欠说此些子。其所谓理发气发者。虽亦极力发挥。而语意终有未备。(气固该形气在内。而但不如直说形气之为较然。显现分晓。)其不能勘覈究极槩多坐此且舍人道当然之目而替换四七为说。同一情也(如以七情四端并言。则喜爱与恻隐。同属仁。怒恶与羞恶。同属义。惧与辞让。同属礼。哀欲与是非。同属智。是非两个情者。晓然可见。特七情是举情之始终首末。四端则其初发之端绪耳。而乃以初发之端与全个情。分占位置。恐自不伦。高峰所谓七情之外。更无四端者。固是。但不经一遭说破此意。故似终无以屈退溪。
焉。是皆理之实状。推之天地四海而准焉者也。帝舜之以一心字。均言于人与道者。圣言微妙。真若造化状物。而朱子或生或原之论。亦可谓善体贴出来矣。若以我东诸贤言之。则逐人分上。各有发明。其义可互备。而长短得失。又随而形焉。盖退溪先生之主于两边说下者。固不害为各溯其所从来矣。然而只如此则可耳。而因之而过于离析。有如理发气随气发理来所云云。则恰若认做个分段先后。其说虽根源于黄勉斋。而终恐不得免二歧之归矣。盖若将此理气而分之乎。则是须实体验于帝舜之旨而参之以朱子说。当以形气与性命之易见其分际者。打开八字。(如孝于亲忠于君。乃自天受来。而为公共道理。不问人己。是于形气甚事。程子所谓不系于人。乃出于天者。正是指此。若饥欲食寒欲衣。精盛思室。则由此形气为一己所独。而他人不知。此与性命无涉。如此分看。其分岂不晓然。)而先生诸说中欠说此些子。其所谓理发气发者。虽亦极力发挥。而语意终有未备。(气固该形气在内。而但不如直说形气之为较然。显现分晓。)其不能勘覈究极槩多坐此且舍人道当然之目而替换四七为说。同一情也(如以七情四端并言。则喜爱与恻隐。同属仁。怒恶与羞恶。同属义。惧与辞让。同属礼。哀欲与是非。同属智。是非两个情者。晓然可见。特七情是举情之始终首末。四端则其初发之端绪耳。而乃以初发之端与全个情。分占位置。恐自不伦。高峰所谓七情之外。更无四端者。固是。但不经一遭说破此意。故似终无以屈退溪。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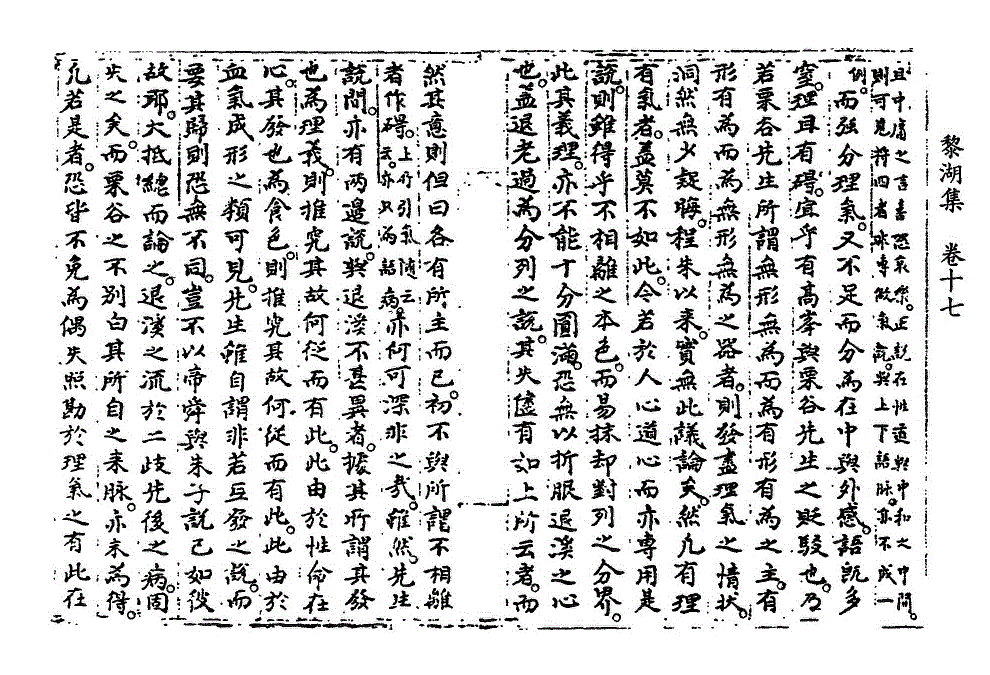 且中庸之言喜怒哀乐。正说在性道与中和之中间。则可见将四者非专做气说。与上下语脉。亦不成一例。)而强分理气。又不足而分为在中与外感。语既多窒。理耳有碍。宜乎有高峰与栗谷先生之贬驳也。乃若栗谷先生所谓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则发尽理气之情状。洞然无少疑晦。程朱以来。实无此议论矣。然凡有理有气者。盖莫不如此。今若于人心道心而亦专用是说。则虽得乎不相离之本色。而易抹却对列之分界。此其义理。亦不能十分圆满。恐无以折服退溪之心也。盖退老过为分列之说。其失尽有如上所云者。而然其意则但曰各有所主而已。初不与所谓不相离者作碍。(上所引气随云云。亦只为语病。)亦何可深非之哉。虽然。先生说间。亦有两边说。与退溪不甚异者。据其所谓其发也为理义。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此由于性命在心。其发也为食色。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此由于血气成形之类可见。先生虽自谓非若互发之说。而要其归则恐无不同。岂不以帝舜与朱子说已如彼故耶。大抵总而论之。退溪之流于二歧先后之病。固失之矣。而栗谷之不别白其所自之来脉。亦未为得。凡若是者。恐皆不免为偶失照勘于理气之有此在
且中庸之言喜怒哀乐。正说在性道与中和之中间。则可见将四者非专做气说。与上下语脉。亦不成一例。)而强分理气。又不足而分为在中与外感。语既多窒。理耳有碍。宜乎有高峰与栗谷先生之贬驳也。乃若栗谷先生所谓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则发尽理气之情状。洞然无少疑晦。程朱以来。实无此议论矣。然凡有理有气者。盖莫不如此。今若于人心道心而亦专用是说。则虽得乎不相离之本色。而易抹却对列之分界。此其义理。亦不能十分圆满。恐无以折服退溪之心也。盖退老过为分列之说。其失尽有如上所云者。而然其意则但曰各有所主而已。初不与所谓不相离者作碍。(上所引气随云云。亦只为语病。)亦何可深非之哉。虽然。先生说间。亦有两边说。与退溪不甚异者。据其所谓其发也为理义。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此由于性命在心。其发也为食色。则推究其故何从而有此。此由于血气成形之类可见。先生虽自谓非若互发之说。而要其归则恐无不同。岂不以帝舜与朱子说已如彼故耶。大抵总而论之。退溪之流于二歧先后之病。固失之矣。而栗谷之不别白其所自之来脉。亦未为得。凡若是者。恐皆不免为偶失照勘于理气之有此在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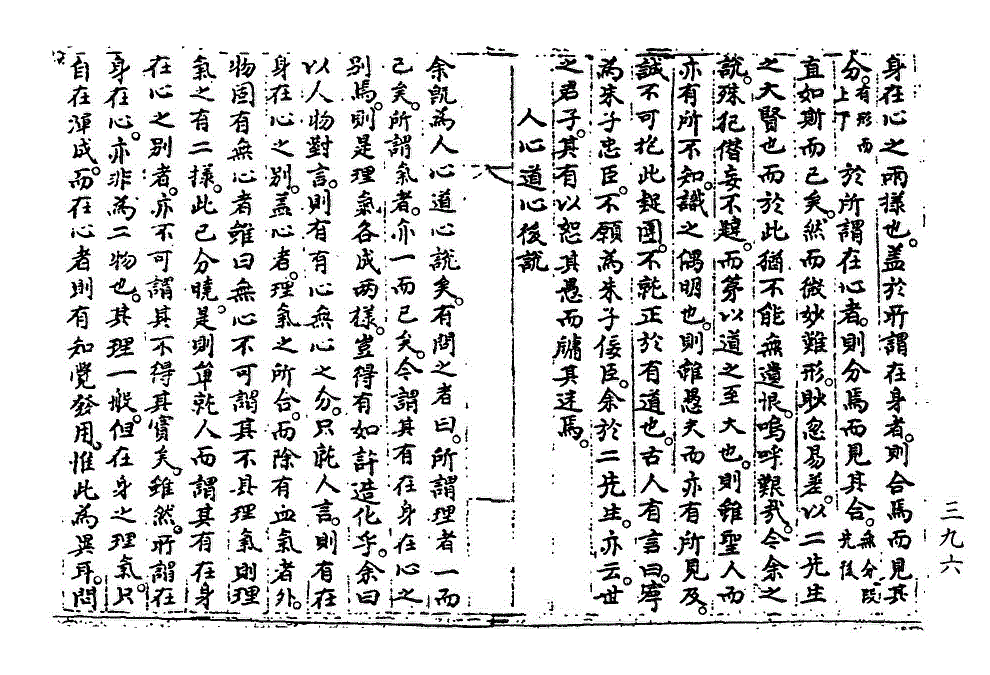 身在心之两㨾也。盖于所谓在身者。则合焉而见其分。(有形而上下。)于所谓在心者。则分焉而见其合。(无分段先后。)直如斯而已矣。然而微妙难形。眇忽易差。以二先生之大贤也而于此犹不能无遗恨。呜呼艰哉。今余之说。殊犯僭妄不韪。而第以道之至大也。则虽圣人而亦有所不知。识之偶明也。则虽愚夫而亦有所见及。诚不可抱此疑团。不就正于有道也。古人有言曰。宁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余于二先生。亦云。世之君子。其有以恕其愚而牗其迷焉。
身在心之两㨾也。盖于所谓在身者。则合焉而见其分。(有形而上下。)于所谓在心者。则分焉而见其合。(无分段先后。)直如斯而已矣。然而微妙难形。眇忽易差。以二先生之大贤也而于此犹不能无遗恨。呜呼艰哉。今余之说。殊犯僭妄不韪。而第以道之至大也。则虽圣人而亦有所不知。识之偶明也。则虽愚夫而亦有所见及。诚不可抱此疑团。不就正于有道也。古人有言曰。宁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余于二先生。亦云。世之君子。其有以恕其愚而牗其迷焉。人心道心后说
余既为人心道心说矣。有问之者曰。所谓理者一而已矣。所谓气者。亦一而已矣。今谓其有在身在心之别焉。则是理气各成两样。岂得有如许造化乎。余曰以人物对言。则有有心无心之分。只就人言。则有在身在心之别。盖心者。理气之所合。而除有血气者外。物固有无心者虽曰无心不可谓其不具理气则理气之有二㨾。此已分晓。是则单就人而谓其有在身在心之别者。亦不可谓其不得其实矣。虽然。所谓在身在心。亦非为二物也。其理一般。但在身之理气。只自在浑成。而在心者则有知觉发用。惟此为异耳。问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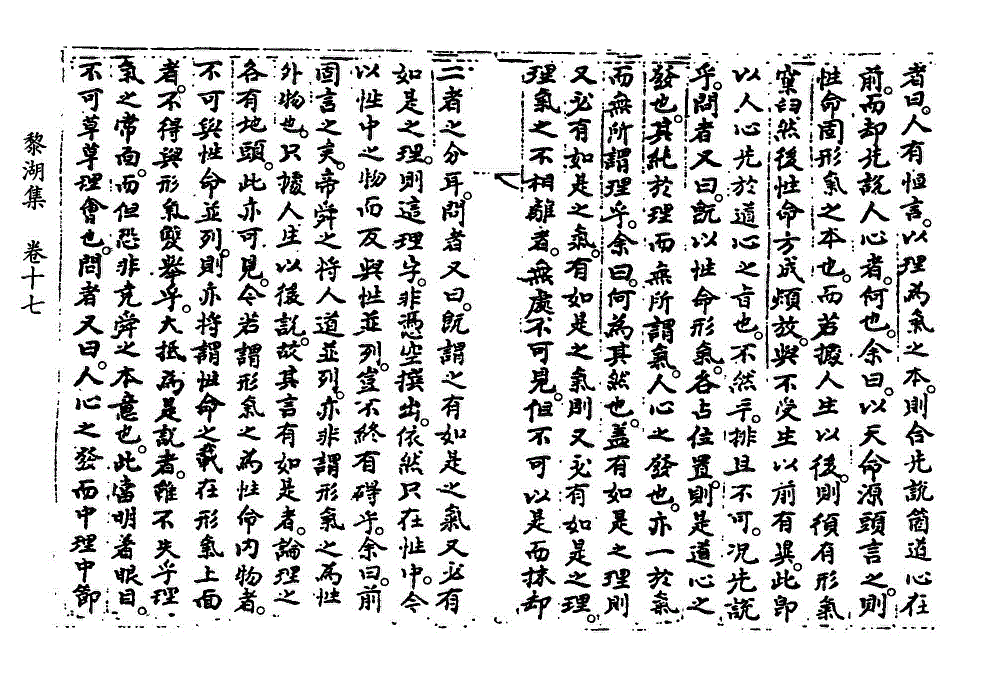 者曰。人有恒言。以理为气之本。则合先说个道心在前。而却先说人心者。何也。余曰。以天命源头言之。则性命固形气之本也。而若据人生以后。则须有形气窠臼然后性命方成频放。与不受生以前有异。此即以人心先于道心之旨也。不然乎。排且不可。况先说乎。问者又曰。既以性命形气。各占位置。则是道心之发也。其纯于理而无所谓气。人心之发也。亦一于气而无所谓理乎。余曰。何为其然也。盖有如是之理则又必有如是之气。有如是之气则又必有如是之理。理气之不相离者。无处不可见。但不可以是而抹却二者之分耳。问者又曰。既谓之有如是之气又必有如是之理。则这理字。非凭空撰出。依然只在性中。今以性中之物而反与性并列。岂不终有碍乎。余曰。前固言之矣。帝舜之将人道并列。亦非谓形气之为性外物也。只据人生以后说。故其言有如是者。论理之各有地头。此亦可见。今若谓形气之为性命内物者。不可与性命并列。则亦将谓性命之载在形气上面者。不得与形气双举乎。大抵为是说者。虽不失乎理气之常面。而但恐非尧舜之本意也。此当明着眼目。不可草草理会也。问者又曰。人心之发而中理中节
者曰。人有恒言。以理为气之本。则合先说个道心在前。而却先说人心者。何也。余曰。以天命源头言之。则性命固形气之本也。而若据人生以后。则须有形气窠臼然后性命方成频放。与不受生以前有异。此即以人心先于道心之旨也。不然乎。排且不可。况先说乎。问者又曰。既以性命形气。各占位置。则是道心之发也。其纯于理而无所谓气。人心之发也。亦一于气而无所谓理乎。余曰。何为其然也。盖有如是之理则又必有如是之气。有如是之气则又必有如是之理。理气之不相离者。无处不可见。但不可以是而抹却二者之分耳。问者又曰。既谓之有如是之气又必有如是之理。则这理字。非凭空撰出。依然只在性中。今以性中之物而反与性并列。岂不终有碍乎。余曰。前固言之矣。帝舜之将人道并列。亦非谓形气之为性外物也。只据人生以后说。故其言有如是者。论理之各有地头。此亦可见。今若谓形气之为性命内物者。不可与性命并列。则亦将谓性命之载在形气上面者。不得与形气双举乎。大抵为是说者。虽不失乎理气之常面。而但恐非尧舜之本意也。此当明着眼目。不可草草理会也。问者又曰。人心之发而中理中节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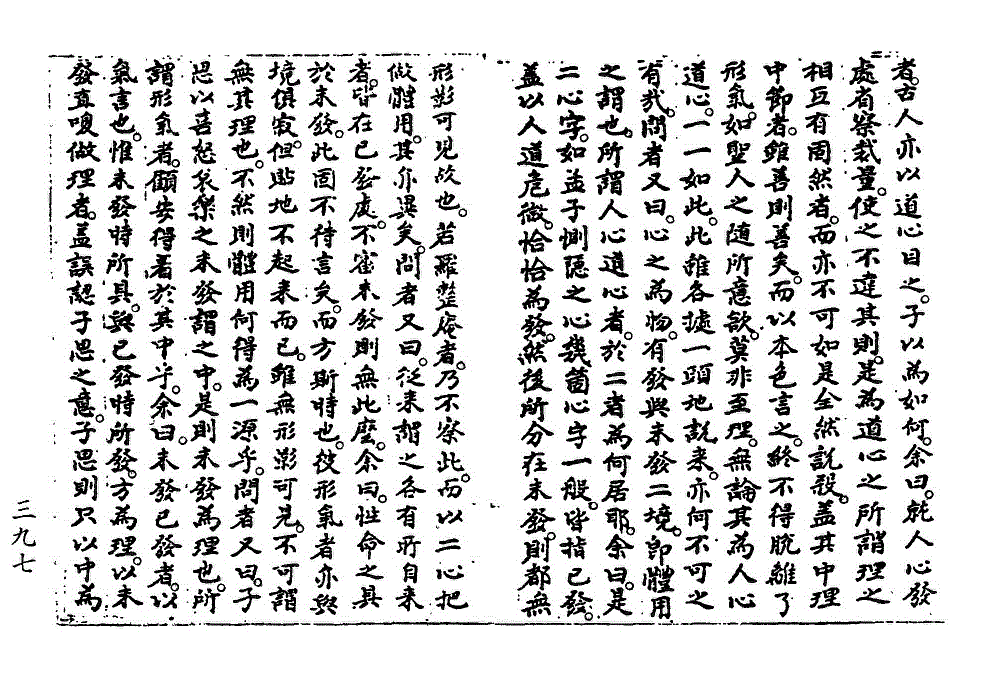 者。古人亦以道心目之。子以为如何。余曰。就人心发处省察裁量。使之不违其则。是为道心之所谓理之相互有固然者。而亦不可如是全然说杀。盖其中理中节者。虽善则善矣。而以本色言之。终不得脱离了形气。如圣人之随所意欲。莫非至理。无论其为人心道心。一一如此。此虽各据一头地说来。亦何不可之有哉。问者又曰。心之为物。有发与未发二境。即体用之谓也。所谓人心道心者。于二者为何居耶。余曰。是二心字。如孟子恻隐之心几个心字一般。皆指已发。盖以人道危微。恰恰为发。然后所分在未发。则都无形影可见故也。若罗整庵者。乃不察此。而以二心把做体用。其亦异矣。问者又曰。从来谓之各有所自来者。皆在已发处。不审未发则无此么。余曰。性命之具于未发。此固不待言矣。而方斯时也。彼形气者亦与境俱寂。但贴地不起来而已。虽无形影可见。不可谓无其理也。不然则体用何得为一源乎。问者又曰。子思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则未发为理也。所谓形气者。顾安得着于其中乎。余曰。未发已发者。以气言也。惟未发时所具。与已发时所发。方为理。以未发直唤做理者。盖误认子思之意。子思则只以中为
者。古人亦以道心目之。子以为如何。余曰。就人心发处省察裁量。使之不违其则。是为道心之所谓理之相互有固然者。而亦不可如是全然说杀。盖其中理中节者。虽善则善矣。而以本色言之。终不得脱离了形气。如圣人之随所意欲。莫非至理。无论其为人心道心。一一如此。此虽各据一头地说来。亦何不可之有哉。问者又曰。心之为物。有发与未发二境。即体用之谓也。所谓人心道心者。于二者为何居耶。余曰。是二心字。如孟子恻隐之心几个心字一般。皆指已发。盖以人道危微。恰恰为发。然后所分在未发。则都无形影可见故也。若罗整庵者。乃不察此。而以二心把做体用。其亦异矣。问者又曰。从来谓之各有所自来者。皆在已发处。不审未发则无此么。余曰。性命之具于未发。此固不待言矣。而方斯时也。彼形气者亦与境俱寂。但贴地不起来而已。虽无形影可见。不可谓无其理也。不然则体用何得为一源乎。问者又曰。子思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则未发为理也。所谓形气者。顾安得着于其中乎。余曰。未发已发者。以气言也。惟未发时所具。与已发时所发。方为理。以未发直唤做理者。盖误认子思之意。子思则只以中为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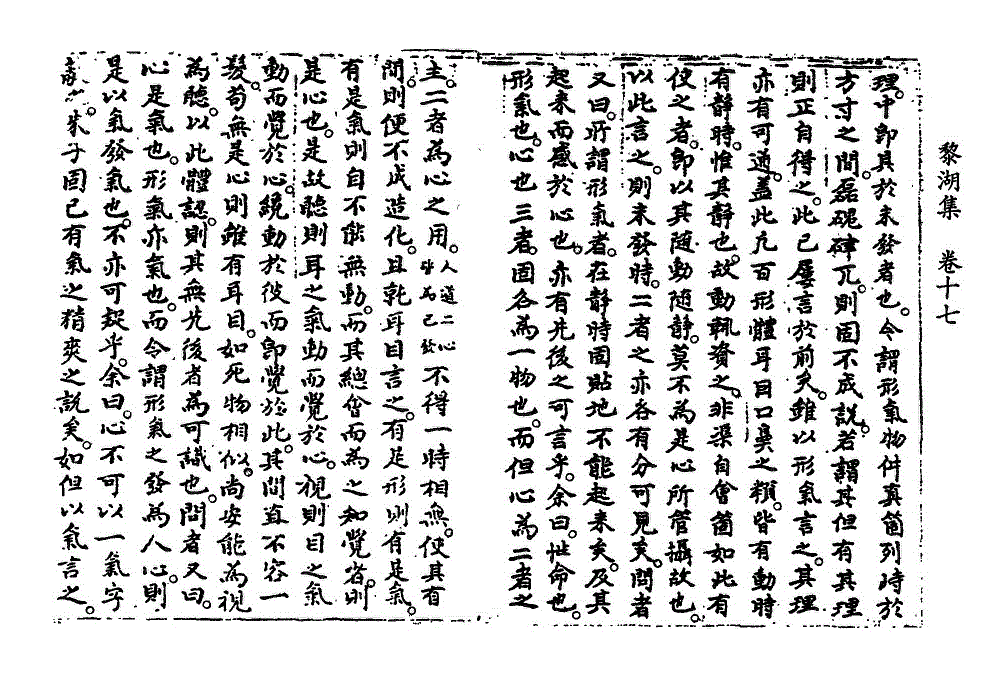 理。中即具于未发者也。今谓形气物件真个列峙于方寸之间。磊磈硉兀。则固不成说。若谓其但有其理则正自得之。此已屡言于前矣。虽以形气言之。其理亦有可通。盖此凡百形体耳目口鼻之类。皆有动时有静时。惟其静也。故动辄资之。非渠自会个如此有使之者。即以其随动随静。莫不为是心所管摄故也。以此言之。则未发时。二者之亦各有分可见矣。问者又曰。所谓形气者。在静时固贴地不能起来矣。及其起来而感于心也。亦有先后之可言乎。余曰。性命也。形气也。心也。三者固各为一物也。而但心为二者之主。二者为心之用。(人道二心皆为已发。)不得一时相无。使其有间。则便不成造化。且就耳目言之。有是形则有是气。有是气则自不能无动。而其总会而为之知觉者。则是心也。是故听则耳之气动而觉于心。视则目之气动而觉于心。才动于彼而即觉于此。其间直不容一发。苟无是心则虽有耳目。如死物相似。尚安能为视为听。以此体认。则其无先后者为可识也。问者又曰。心是气也。形气亦气也。而今谓形气之发为人心。则是以气发气也。不亦可疑乎。余曰。心不可以一气字蔽之。朱子固已有气之精爽之说矣。如但以气言之。
理。中即具于未发者也。今谓形气物件真个列峙于方寸之间。磊磈硉兀。则固不成说。若谓其但有其理则正自得之。此已屡言于前矣。虽以形气言之。其理亦有可通。盖此凡百形体耳目口鼻之类。皆有动时有静时。惟其静也。故动辄资之。非渠自会个如此有使之者。即以其随动随静。莫不为是心所管摄故也。以此言之。则未发时。二者之亦各有分可见矣。问者又曰。所谓形气者。在静时固贴地不能起来矣。及其起来而感于心也。亦有先后之可言乎。余曰。性命也。形气也。心也。三者固各为一物也。而但心为二者之主。二者为心之用。(人道二心皆为已发。)不得一时相无。使其有间。则便不成造化。且就耳目言之。有是形则有是气。有是气则自不能无动。而其总会而为之知觉者。则是心也。是故听则耳之气动而觉于心。视则目之气动而觉于心。才动于彼而即觉于此。其间直不容一发。苟无是心则虽有耳目。如死物相似。尚安能为视为听。以此体认。则其无先后者为可识也。问者又曰。心是气也。形气亦气也。而今谓形气之发为人心。则是以气发气也。不亦可疑乎。余曰。心不可以一气字蔽之。朱子固已有气之精爽之说矣。如但以气言之。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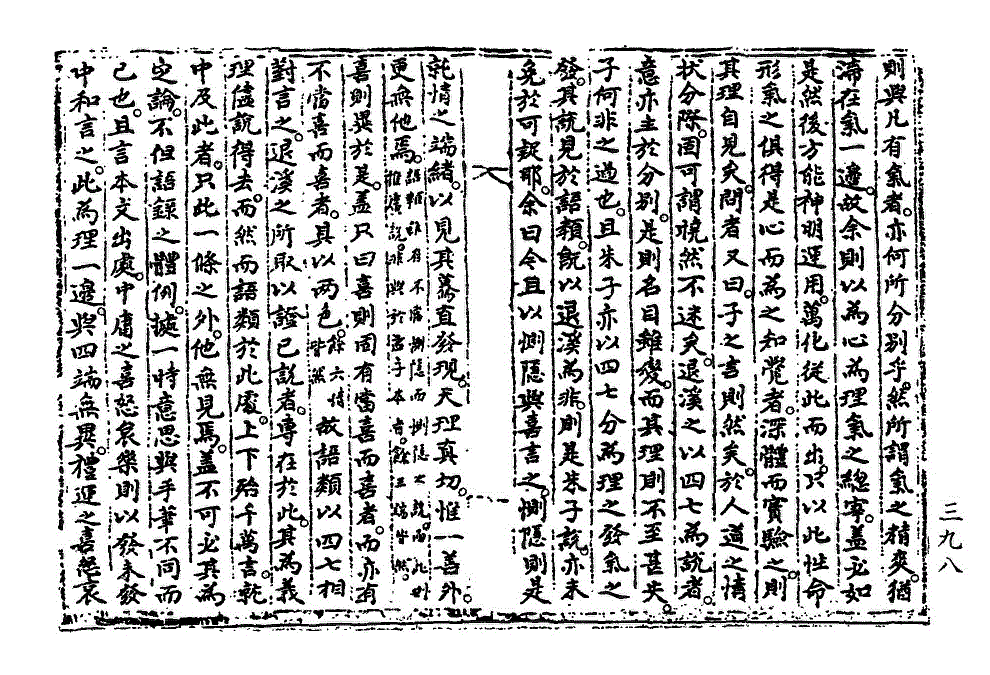 则与凡有气者。亦何所分别乎。然所谓气之精爽。犹滞在气一边。故余则以为心为理气之总宰。盖必如是然后方能神明运用。万化从此而出。只以此性命形气之俱得是心而为之知觉者。深体而实验之。则其理自见矣。问者又曰。子之言则然矣。于人道之情状分际。固可谓晓然不迷矣。退溪之以四七为说者。意亦主于分别。是则名目虽变。而其理则不至甚失。子何非之过也。且朱子亦以四七分为理之发气之发。其说见于语类。既以退溪为非。则是朱子说。亦未免于可疑耶。余曰今且以恻隐与喜言之。恻隐则是就情之端绪。以见其蓦直发现。天理真切。惟一善外。更无他焉。(语类虽有不当恻隐而恻隐之说。而此则推广说。非与于孟子本旨。馀三端皆然。)喜则异于是。盖只曰喜则固有当喜而喜者。而亦有不当喜而喜者。具以两色。(馀六情皆然。)故语类以四七相对言之。退溪之所取以證己说者。专在于此。其为义理尽说得去。而然而语类于此处。上下殆千万言。就中及此者。只此一条之外。他无见焉。盖不可必其为定论。不但语录之体例。据一时意思与手笔不同而已也。且言本文出处。中庸之喜怒哀乐则以发未发中和言之。此为理一边。与四端无异。礼运之喜怒哀
则与凡有气者。亦何所分别乎。然所谓气之精爽。犹滞在气一边。故余则以为心为理气之总宰。盖必如是然后方能神明运用。万化从此而出。只以此性命形气之俱得是心而为之知觉者。深体而实验之。则其理自见矣。问者又曰。子之言则然矣。于人道之情状分际。固可谓晓然不迷矣。退溪之以四七为说者。意亦主于分别。是则名目虽变。而其理则不至甚失。子何非之过也。且朱子亦以四七分为理之发气之发。其说见于语类。既以退溪为非。则是朱子说。亦未免于可疑耶。余曰今且以恻隐与喜言之。恻隐则是就情之端绪。以见其蓦直发现。天理真切。惟一善外。更无他焉。(语类虽有不当恻隐而恻隐之说。而此则推广说。非与于孟子本旨。馀三端皆然。)喜则异于是。盖只曰喜则固有当喜而喜者。而亦有不当喜而喜者。具以两色。(馀六情皆然。)故语类以四七相对言之。退溪之所取以證己说者。专在于此。其为义理尽说得去。而然而语类于此处。上下殆千万言。就中及此者。只此一条之外。他无见焉。盖不可必其为定论。不但语录之体例。据一时意思与手笔不同而已也。且言本文出处。中庸之喜怒哀乐则以发未发中和言之。此为理一边。与四端无异。礼运之喜怒哀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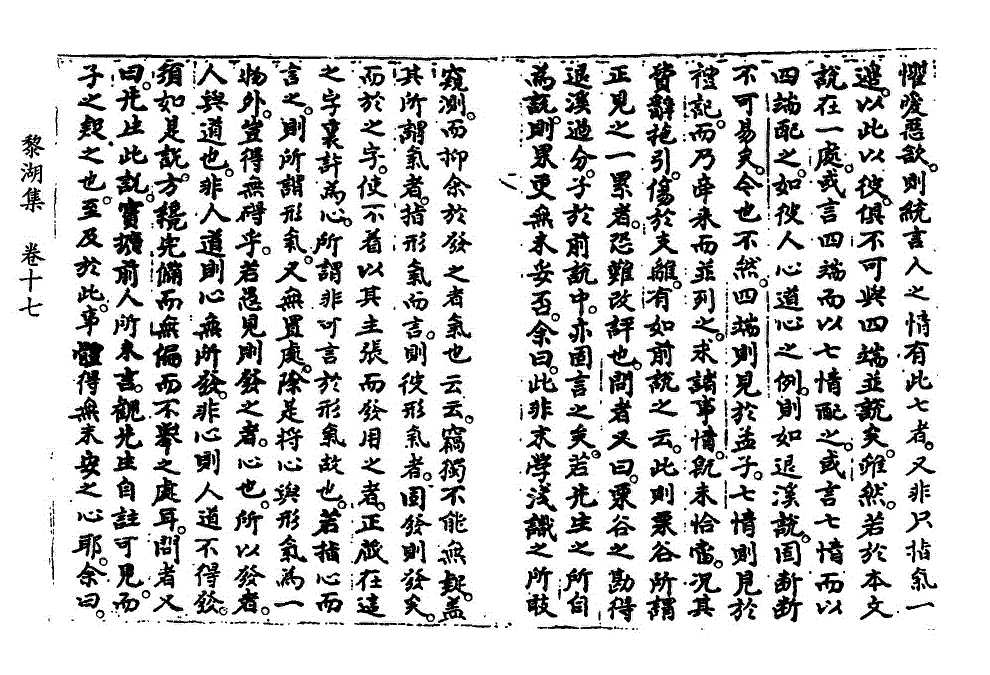 惧爱恶欲。则统言人之情有此七者。又非只指气一边。以此以彼。俱不可与四端并说矣。虽然。若于本文说在一处。或言四端而以七情配之。或言七情而以四端配之。如彼人心道心之例。则如退溪说。固断断不可易矣。今也不然。四端则见于孟子。七情则见于礼记。而乃牵来而并列之。求诸事情。既未恰当。况其费辞拖引。伤于支离。有如前说之云。此则栗谷所谓正见之一累者。恐难改评也。问者又曰。栗谷之勘得退溪过分。子于前说中。亦固言之矣。若先生之所自为说。则果更无未妥否。余曰。此非末学浅识之所敢窥测。而抑余于发之者气也云云。窃独不能无疑。盖其所谓气者。指形气而言。则彼形气者。固发则发矣。而于之字。使不着以其主张而发用之者。正藏在这之字里许为心。所谓非可言于形气故也。若指心而言之。则所谓形气。又无置处。除是将心与形气为一物外。岂得无碍乎。若愚见则发之者。心也。所以发者。人与道也。非人道则心无所发。非心则人道不得发。须如是说。方才完备而无偏而不举之处耳。问者又曰。先生此说。实扩前人所未言。观先生自注可见。而子之疑之也。至及于此。事体得无未安之心耶。余曰。
惧爱恶欲。则统言人之情有此七者。又非只指气一边。以此以彼。俱不可与四端并说矣。虽然。若于本文说在一处。或言四端而以七情配之。或言七情而以四端配之。如彼人心道心之例。则如退溪说。固断断不可易矣。今也不然。四端则见于孟子。七情则见于礼记。而乃牵来而并列之。求诸事情。既未恰当。况其费辞拖引。伤于支离。有如前说之云。此则栗谷所谓正见之一累者。恐难改评也。问者又曰。栗谷之勘得退溪过分。子于前说中。亦固言之矣。若先生之所自为说。则果更无未妥否。余曰。此非末学浅识之所敢窥测。而抑余于发之者气也云云。窃独不能无疑。盖其所谓气者。指形气而言。则彼形气者。固发则发矣。而于之字。使不着以其主张而发用之者。正藏在这之字里许为心。所谓非可言于形气故也。若指心而言之。则所谓形气。又无置处。除是将心与形气为一物外。岂得无碍乎。若愚见则发之者。心也。所以发者。人与道也。非人道则心无所发。非心则人道不得发。须如是说。方才完备而无偏而不举之处耳。问者又曰。先生此说。实扩前人所未言。观先生自注可见。而子之疑之也。至及于此。事体得无未安之心耶。余曰。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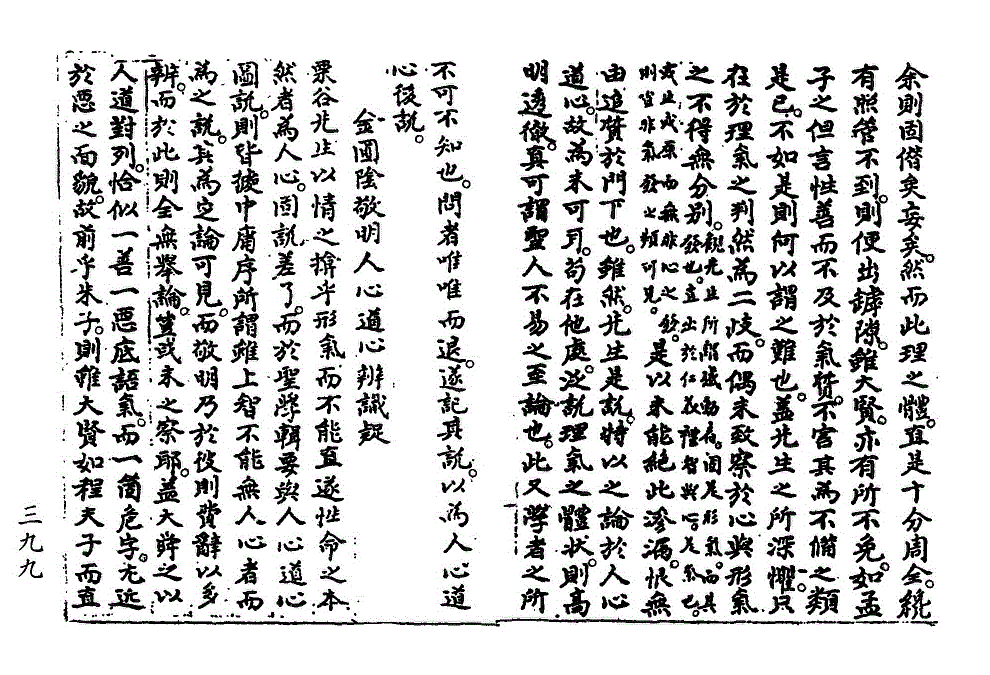 余则固僭矣妄矣。然而此理之体。直是十分周全。才有照管不到。则便出罅隙。虽大贤。亦有所不免。如孟子之但言性善而不及于气质。不害其为不备之类是已。不如是则何以谓之难也。盖先生之所深惧。只在于理气之判然为二歧。而偶未致察于心与形气之不得无分别。(观先生所谓感动者。固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与心。是气也。或生或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之类可见。)是以未能绝此渗漏。恨无由追质于门下也。虽然。先生是说。特以之论于人心道心。故为未可耳。苟在他处。泛说理气之体状。则高明透彻。真可谓圣人不易之至论也。此又学者之所不可不知也。问者唯唯而退。遂记其说。以为人心道心后说。
余则固僭矣妄矣。然而此理之体。直是十分周全。才有照管不到。则便出罅隙。虽大贤。亦有所不免。如孟子之但言性善而不及于气质。不害其为不备之类是已。不如是则何以谓之难也。盖先生之所深惧。只在于理气之判然为二歧。而偶未致察于心与形气之不得无分别。(观先生所谓感动者。固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与心。是气也。或生或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之类可见。)是以未能绝此渗漏。恨无由追质于门下也。虽然。先生是说。特以之论于人心道心。故为未可耳。苟在他处。泛说理气之体状。则高明透彻。真可谓圣人不易之至论也。此又学者之所不可不知也。问者唯唯而退。遂记其说。以为人心道心后说。金圃阴敬明人心道心辨识疑
栗谷先生以情之掩乎形气而不能直遂性命之本然者为人心。固说差了。而于圣学辑要与人心道心图说。则皆据中庸序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而为之说。其为定论可见。而敬明乃于彼则费辞以多辨。而于此则全无举论。岂或未之察耶。盖大舜之以人道对列。恰似一善一恶底语气。而一个危字。尤近于恶之面貌。故前乎朱子。则虽大贤如程夫子而直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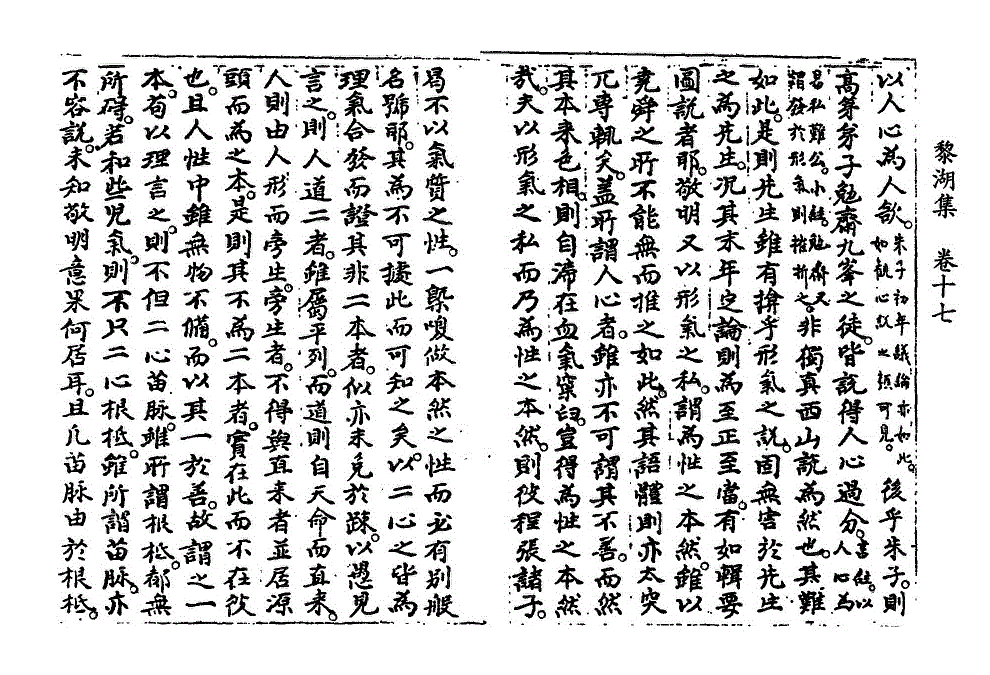 以人心为人欲。(朱子初年议论亦如此。如观心说之类可见。)后乎朱子。则高第弟子勉斋九峰之徒。皆说得人心过分。(书注。以人心为易私难公。小注。勉斋又谓发于形气则摧折之。)非独真西山说为然也。其难如此。是则先生虽有掩乎形气之说。固无害于先生之为先生。况其末年定论则为至正至当。有如辑要图说者耶。敬明又以形气之私。谓为性之本然。虽以尧舜之所不能无而推之如此。然其语体则亦太突兀专辄矣。盖所谓人心者。虽亦不可谓其不善。而然其本来色相。则自滞在血气窠臼。岂得为性之本然哉。夫以形气之私而乃为性之本然。则彼程张诸子。曷不以气质之性。一槩唤做本然之性而必有别般名号耶。其为不可据此而可知之矣。以二心之皆为理气合发而證其非二本者。似亦未免于疏。以愚见言之。则人道二者。虽属平列。而道则自天命而直来。人则由人形而旁生。旁生者。不得与直来者并居源头而为之本。是则其不为二本者。实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人性中虽无物不备。而以其一于善。故谓之一本。苟以理言之。则不但二心苗脉。虽所谓根柢。都无所碍。若和些儿气。则不只二心根柢。虽所谓苗脉。亦不容说。未知敬明意果何居耳。且凡苗脉由于根柢。
以人心为人欲。(朱子初年议论亦如此。如观心说之类可见。)后乎朱子。则高第弟子勉斋九峰之徒。皆说得人心过分。(书注。以人心为易私难公。小注。勉斋又谓发于形气则摧折之。)非独真西山说为然也。其难如此。是则先生虽有掩乎形气之说。固无害于先生之为先生。况其末年定论则为至正至当。有如辑要图说者耶。敬明又以形气之私。谓为性之本然。虽以尧舜之所不能无而推之如此。然其语体则亦太突兀专辄矣。盖所谓人心者。虽亦不可谓其不善。而然其本来色相。则自滞在血气窠臼。岂得为性之本然哉。夫以形气之私而乃为性之本然。则彼程张诸子。曷不以气质之性。一槩唤做本然之性而必有别般名号耶。其为不可据此而可知之矣。以二心之皆为理气合发而證其非二本者。似亦未免于疏。以愚见言之。则人道二者。虽属平列。而道则自天命而直来。人则由人形而旁生。旁生者。不得与直来者并居源头而为之本。是则其不为二本者。实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人性中虽无物不备。而以其一于善。故谓之一本。苟以理言之。则不但二心苗脉。虽所谓根柢。都无所碍。若和些儿气。则不只二心根柢。虽所谓苗脉。亦不容说。未知敬明意果何居耳。且凡苗脉由于根柢。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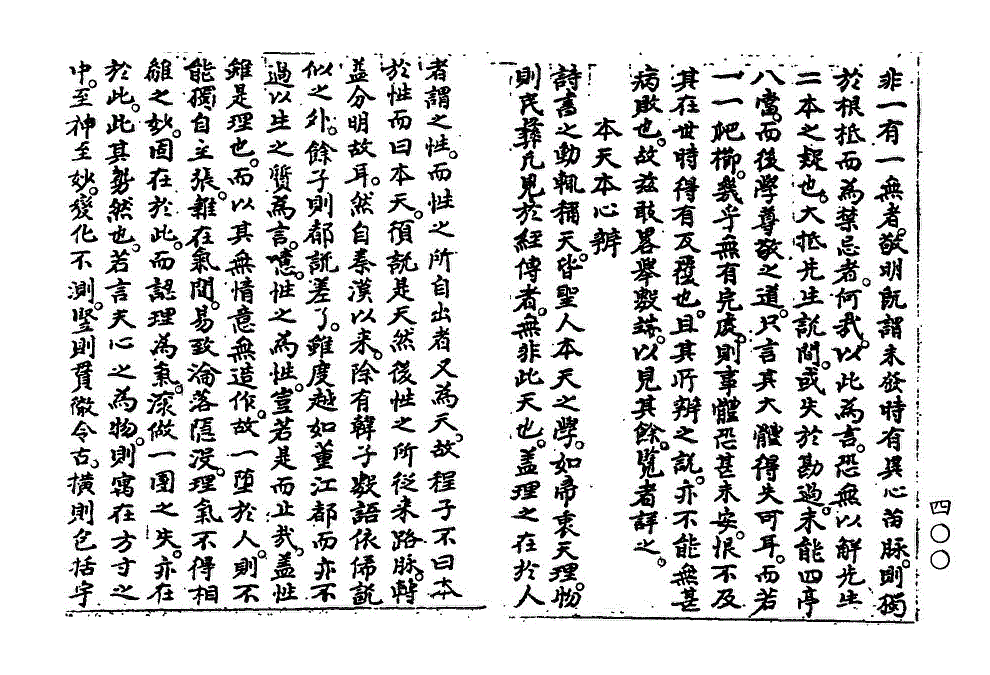 非一有一无者。敬明既谓未发时有异心苗脉。则独于根柢而为禁忌者。何哉。以此为言。恐无以解先生二本之疑也。大抵先生说间。或失于勘过。未能四亭八当。而后学尊敬之道。只言其大体得失可耳。而若一一爬栉。几乎无有完处。则事体恐甚未安。恨不及其在世时得有反覆也。且其所辨之说。亦不能无甚病败也。故玆敢略举数端。以见其馀。览者详之。
非一有一无者。敬明既谓未发时有异心苗脉。则独于根柢而为禁忌者。何哉。以此为言。恐无以解先生二本之疑也。大抵先生说间。或失于勘过。未能四亭八当。而后学尊敬之道。只言其大体得失可耳。而若一一爬栉。几乎无有完处。则事体恐甚未安。恨不及其在世时得有反覆也。且其所辨之说。亦不能无甚病败也。故玆敢略举数端。以见其馀。览者详之。本天本心辨
诗书之动辄称天。皆圣人本天之学。如帝衷天理。物则民彝凡见于经传者。无非此天也。盖理之在于人者谓之性。而性之所自出者又为天。故程子不曰本于性而曰本天。须说是天然后性之所从来路脉。转益分明故耳。然自秦汉以来。除有韩子数语依俙说似之外。馀子则都说差了。虽度越如董江都而亦不过以生之质为言。噫。性之为性。岂若是而止哉。盖性虽是理也。而以其无情意无造作。故一堕于人。则不能独自主张。杂在气间。易致沦落隐没。理气不得相离之妙。固在于此。而认理为气。滚做一团之失。亦在于此。此其势然也。若言夫心之为物。则寓在方寸之中。至神至妙。变化不测。竖则贯彻今古。横则包括宇
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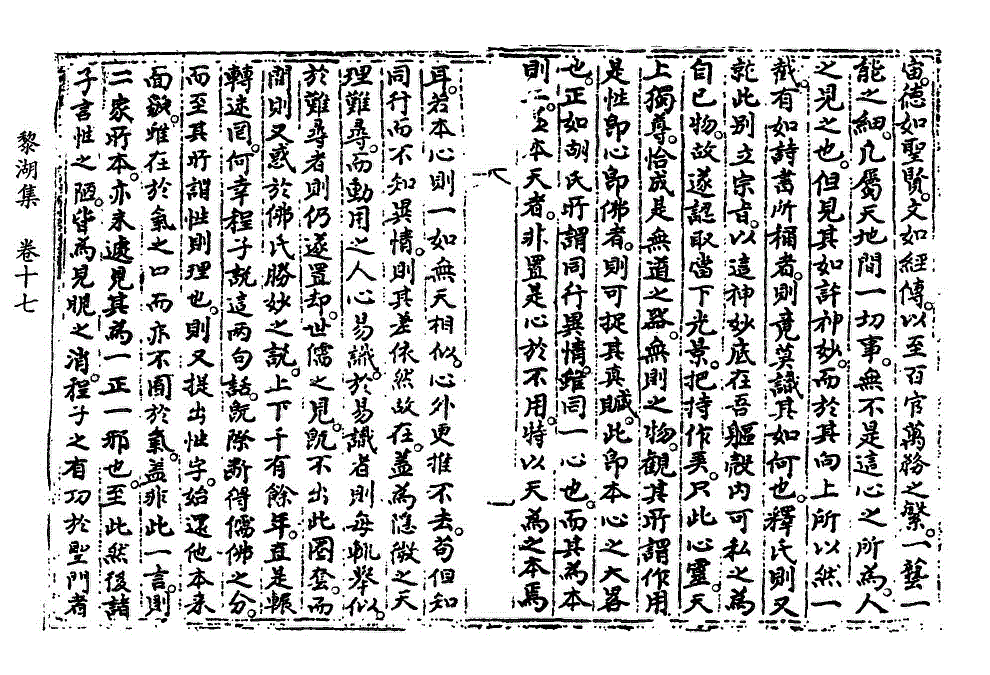 宙。德如圣贤。文如经传。以至百官万务之繁。一艺一能之细。凡属天地间一切事。无不是这心之所为。人之见之也。但见其如许神妙。而于其向上所以然一截。有如诗书所称者。则竟莫识其如何也。释氏则又就此别立宗旨。以这神妙底在吾躯壳内可私之为自己物。故遂认取当下光景。把持作弄。只此心灵。天上独尊。恰成是无道之器。无则之物。观其所谓作用是性即心即佛者。则可捉其真赃。此即本心之大略也。正如胡氏所谓同行异情。虽同一心也。而其为本则二。盖本天者。非置是心于不用。特以天为之本焉耳。若本心则一如无天相似。心外更推不去。苟但知同行而不知异情。则其差依然故在。盖为隐微之天理难寻。而动用之人心易识。于易识者则每辄举似。于难寻者则仍遂置却。世儒之见。既不出此圈套。而间则又惑于佛氏胜妙之说。上下千有馀年。直是辗转迷罔。何幸程子说这两句话。既际断得儒佛之分。而至其所谓性则理也。则又提出性字。始还他本来面貌。虽在于气之口而亦不囿于气。盖非此一言。则二家所本。亦未遽见其为一正一邪也。至此然后诸子言性之陋。皆为见晛之消。程子之有功于圣门者
宙。德如圣贤。文如经传。以至百官万务之繁。一艺一能之细。凡属天地间一切事。无不是这心之所为。人之见之也。但见其如许神妙。而于其向上所以然一截。有如诗书所称者。则竟莫识其如何也。释氏则又就此别立宗旨。以这神妙底在吾躯壳内可私之为自己物。故遂认取当下光景。把持作弄。只此心灵。天上独尊。恰成是无道之器。无则之物。观其所谓作用是性即心即佛者。则可捉其真赃。此即本心之大略也。正如胡氏所谓同行异情。虽同一心也。而其为本则二。盖本天者。非置是心于不用。特以天为之本焉耳。若本心则一如无天相似。心外更推不去。苟但知同行而不知异情。则其差依然故在。盖为隐微之天理难寻。而动用之人心易识。于易识者则每辄举似。于难寻者则仍遂置却。世儒之见。既不出此圈套。而间则又惑于佛氏胜妙之说。上下千有馀年。直是辗转迷罔。何幸程子说这两句话。既际断得儒佛之分。而至其所谓性则理也。则又提出性字。始还他本来面貌。虽在于气之口而亦不囿于气。盖非此一言。则二家所本。亦未遽见其为一正一邪也。至此然后诸子言性之陋。皆为见晛之消。程子之有功于圣门者黎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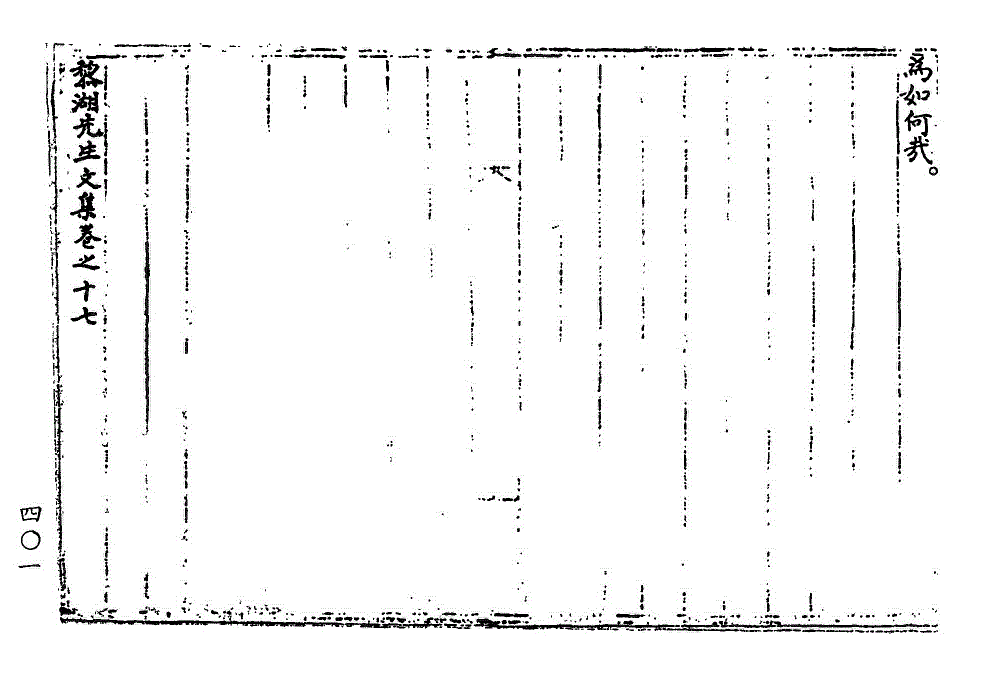 为如何哉。
为如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