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x 页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书
书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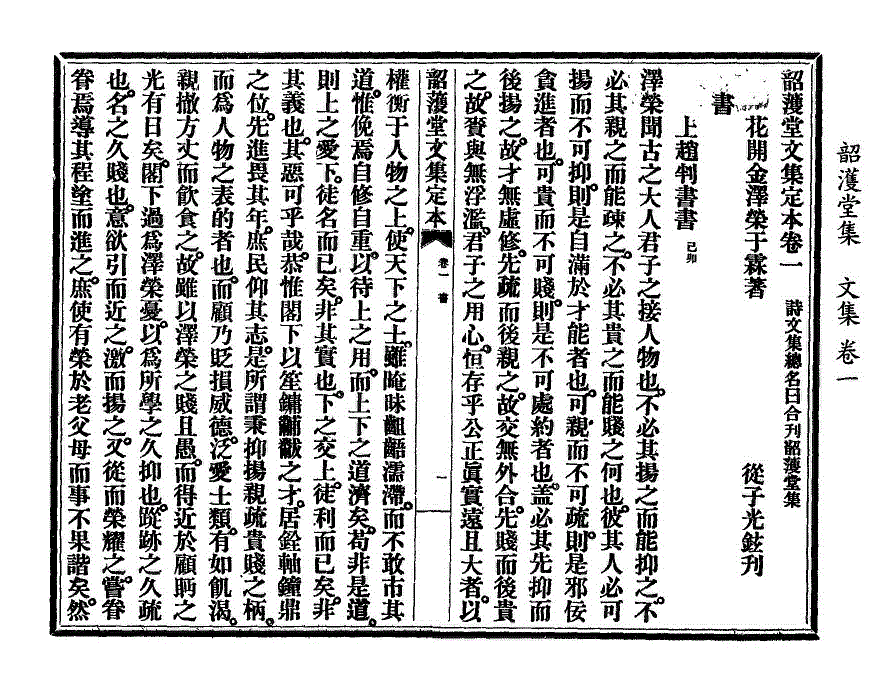 上赵判书书(己卯)
上赵判书书(己卯)泽荣闻古之大人君子之接人物也。不必其扬之而能抑之。不必其亲之而能疏之。不必其贵之而能贱之何也。彼其人必可扬而不可抑。则是自满于才能者也。可亲而不可疏。则是邪佞贪进者也。可贵而不可贱。则是不可处约者也。盖必其先抑而后扬之。故才无虚修。先疏而后亲之。故交无外合。先贱而后贵之。故赉与无浮滥。君子之用心。恒存乎公正真实远且大者。以权衡于人物之上。使天下之士。虽晻昧龃龉濡滞。而不敢市其道。惟俛焉自修自重。以待上之用。而上下之道济矣。苟非是道。则上之爱下。徒名而已矣。非其实也。下之交上。徒利而已矣。非其义也。其恶可乎哉。恭惟阁下以笙镛黼黻之才。居铨轴钟鼎之位。先进畏其年。庶民仰其志。是所谓秉抑扬亲疏贵贱之柄。而为人物之表的者也。而顾乃贬损威德。泛爱士类。有如饥渴。亲撤方丈而饮食之。故虽以泽荣之贱且愚。而得近于顾眄之光有日矣。阁下过为泽荣忧。以为所学之久抑也。踪迹之久疏也。名之久贱也。意欲引而近之。激而扬之。又从而荣耀之。尝眷眷焉导其程涂而进之。庶使有荣于老父母而事不果谐矣。然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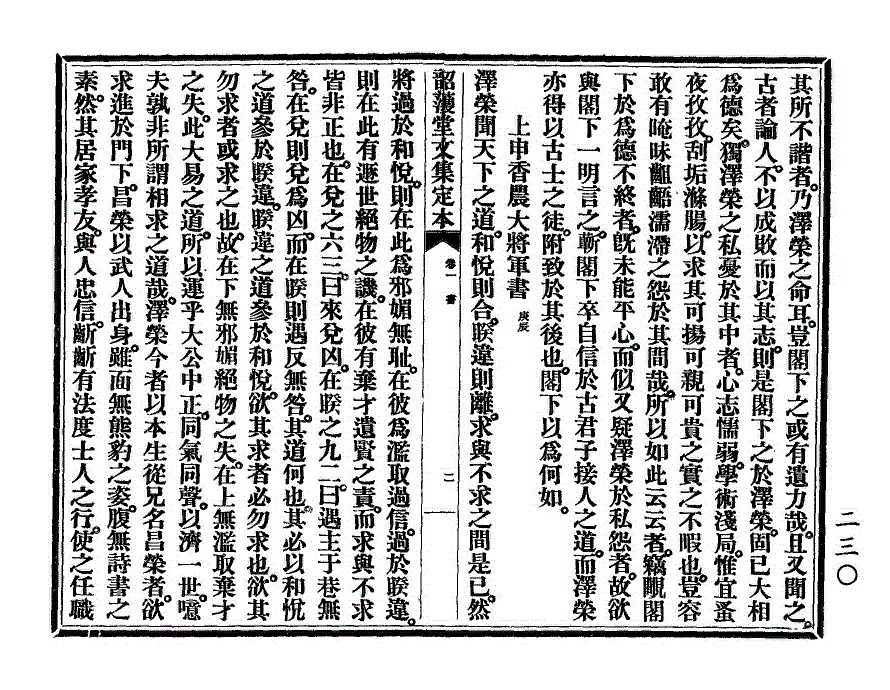 其所不谐者。乃泽荣之命耳。岂阁下之或有遗力哉。且又闻之。古者论人。不以成败而以其志。则是阁下之于泽荣。固已大相为德矣。独泽荣之私忧于其中者。心志懦弱。学术浅局。惟宜蚤夜孜孜。刮垢涤肠。以求其可扬可亲可贵之实之不暇也。岂容敢有晻昧龃龉濡滞之怨于其间哉。所以如此云云者。窃覸阁下于为德不终者。既未能平心。而似又疑泽荣于私怨者。故欲与阁下一明言之。蕲阁下卒自信于古君子接人之道。而泽荣亦得以古士之徒。附致于其后也。阁下以为何如。
其所不谐者。乃泽荣之命耳。岂阁下之或有遗力哉。且又闻之。古者论人。不以成败而以其志。则是阁下之于泽荣。固已大相为德矣。独泽荣之私忧于其中者。心志懦弱。学术浅局。惟宜蚤夜孜孜。刮垢涤肠。以求其可扬可亲可贵之实之不暇也。岂容敢有晻昧龃龉濡滞之怨于其间哉。所以如此云云者。窃覸阁下于为德不终者。既未能平心。而似又疑泽荣于私怨者。故欲与阁下一明言之。蕲阁下卒自信于古君子接人之道。而泽荣亦得以古士之徒。附致于其后也。阁下以为何如。上申香农大将军书(庚辰)
泽荣闻天下之道。和悦则合。睽违则离。求与不求之间是已。然将过于和悦。则在此为邪媚无耻。在彼为滥取过信。过于睽违。则在此有遁世绝物之讥。在彼有弃才遗贤之责。而求与不求皆非正也。在兑之六三。曰来兑凶。在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无咎。在兑则兑为凶。而在睽则遇反无咎。其道何也。其必以和悦之道参于睽违。睽违之道参于和悦。欲其求者必勿求也。欲其勿求者或求之也。故在下无邪媚绝物之失。在上无滥取弃才之失。此大易之道。所以运乎大公中正。同气同声。以济一世。噫夫孰非所谓相求之道哉。泽荣今者以本生从兄名昌荣者。欲求进于门下。昌荣以武人出身。虽面无熊豹之姿。腹无诗书之素。然其居家孝友。与人忠信。龂龂有法度士人之行。使之任职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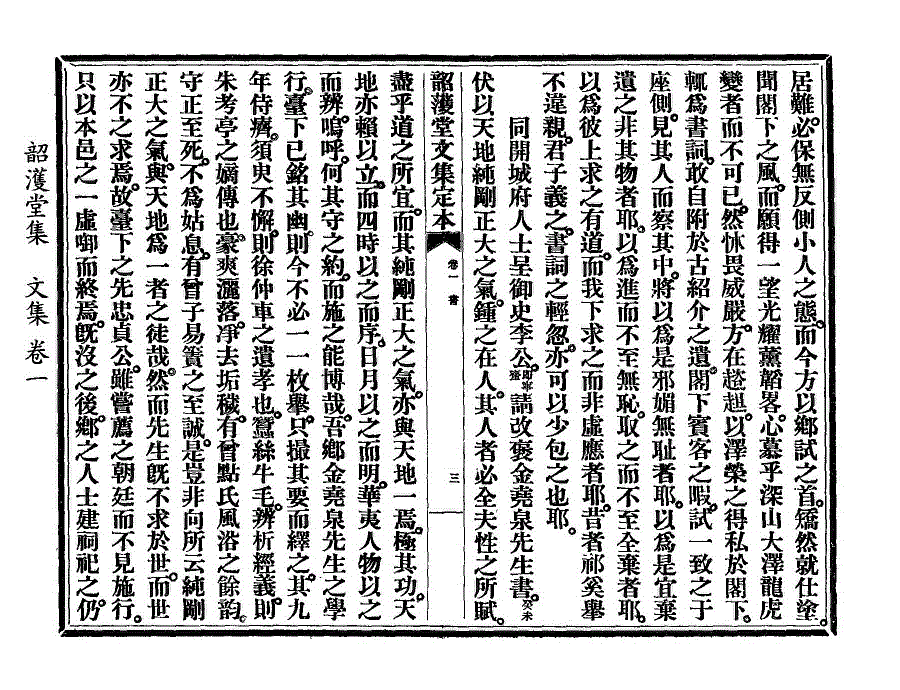 居难。必保无反侧小人之态。而今方以乡试之首。矫然就仕涂。闻阁下之风。而愿得一望光耀薰韬略。心慕乎深山大泽龙虎变者而不可已。然怵畏威严。方在趑趄。以泽荣之得私于阁下。辄为书词。敢自附于古绍介之遗。阁下宾客之暇。试一致之于座侧。见其人而察其中。将以为是邪媚无耻者耶。以为是宜弃遗之非其物者耶。以为进而不至无耻。取之而不至全弃者耶。以为彼上求之有道。而我下求之而非虚应者耶。昔者祁奚举不违亲。君子义之。书词之轻忽。亦可以少包之也耶。
居难。必保无反侧小人之态。而今方以乡试之首。矫然就仕涂。闻阁下之风。而愿得一望光耀薰韬略。心慕乎深山大泽龙虎变者而不可已。然怵畏威严。方在趑趄。以泽荣之得私于阁下。辄为书词。敢自附于古绍介之遗。阁下宾客之暇。试一致之于座侧。见其人而察其中。将以为是邪媚无耻者耶。以为是宜弃遗之非其物者耶。以为进而不至无耻。取之而不至全弃者耶。以为彼上求之有道。而我下求之而非虚应者耶。昔者祁奚举不违亲。君子义之。书词之轻忽。亦可以少包之也耶。同开城府人士呈御史李公。(即宁斋)请改褒金尧泉先生书。(癸未)
伏以天地纯刚正大之气。钟之在人。其人者必全夫性之所赋。尽乎道之所宜。而其纯刚正大之气。亦与天地一焉。极其功。天地亦赖以立。而四时以之而序。日月以之而明。华夷人物以之而辨。呜呼。何其守之约。而施之能博哉。吾乡金尧泉先生之学行。台下已铭其幽。则今不必一一枚举。只撮其要而绎之。其九年侍癠。须臾不懈。则徐仲车之遗孝也。蚕丝牛毛。辨析经义。则朱考亭之嫡传也。豪爽洒落。净去垢秽。有曾点氏风浴之馀韵。守正至死。不为姑息。有曾子易箦之至诚。是岂非向所云纯刚正大之气。与天地为一者之徒哉。然而先生既不求于世。而世亦不之求焉。故台下之先忠贞公。虽尝荐之朝廷而不见施行。只以本邑之一虚衔而终焉。既没之后。乡之人士建祠祀之。仍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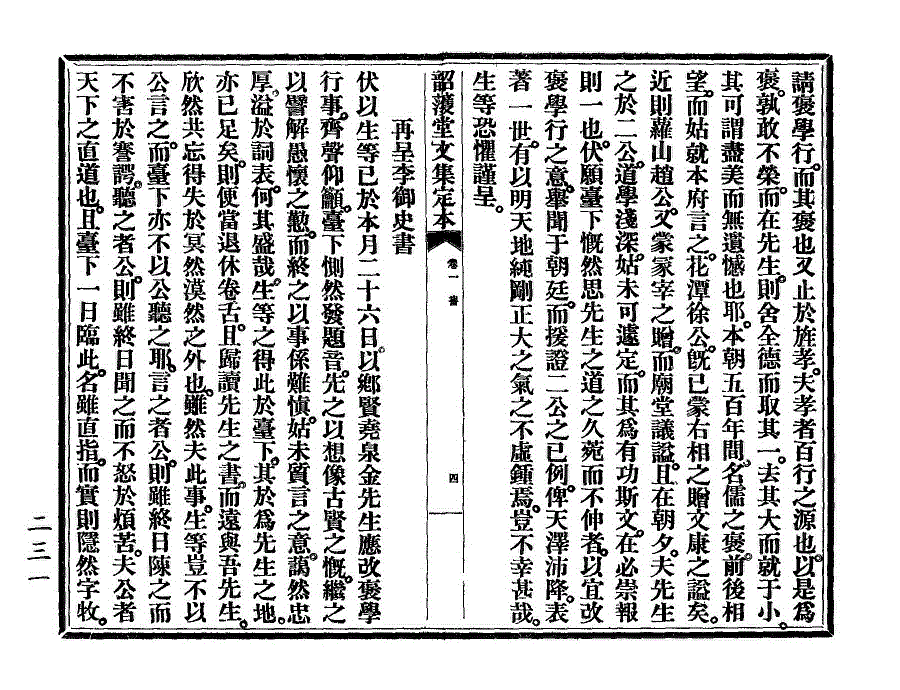 请褒学行。而其褒也又止于旌孝。夫孝者百行之源也。以是为褒。孰敢不荣。而在先生。则舍全德而取其一。去其大而就于小。其可谓尽美而无遗憾也耶。本朝五百年间。名儒之褒。前后相望。而姑就本府言之。花潭徐公。既已蒙右相之赠文康之谥矣。近则萝山赵公。又蒙冢宰之赠。而庙堂议谥。且在朝夕。夫先生之于二公。道学浅深。姑未可遽定。而其为有功斯文。在必崇报则一也。伏愿台下慨然思先生之道之久菀而不伸者。以宜改褒学行之意。举闻于朝廷。而援證二公之已例。俾天泽沛降。表著一世。有以明天地纯刚正大之气之不虚钟焉。岂不幸甚哉。生等恐惧谨呈。
请褒学行。而其褒也又止于旌孝。夫孝者百行之源也。以是为褒。孰敢不荣。而在先生。则舍全德而取其一。去其大而就于小。其可谓尽美而无遗憾也耶。本朝五百年间。名儒之褒。前后相望。而姑就本府言之。花潭徐公。既已蒙右相之赠文康之谥矣。近则萝山赵公。又蒙冢宰之赠。而庙堂议谥。且在朝夕。夫先生之于二公。道学浅深。姑未可遽定。而其为有功斯文。在必崇报则一也。伏愿台下慨然思先生之道之久菀而不伸者。以宜改褒学行之意。举闻于朝廷。而援證二公之已例。俾天泽沛降。表著一世。有以明天地纯刚正大之气之不虚钟焉。岂不幸甚哉。生等恐惧谨呈。再呈李御史书
伏以生等已于本月二十六日。以乡贤尧泉金先生应改褒学行事。齐声仰吁。台下恻然发题音。先之以想像古贤之慨。继之以譬解愚怀之勤。而终之以事系难慎。姑未质言之意。蔼然忠厚。溢于词表。何其盛哉。生等之得此于台下。其于为先生之地。亦已足矣。则便当退休卷舌。且归读先生之书。而远与吾先生。欣然共忘得失于冥然漠然之外也。虽然夫此事。生等岂不以公言之。而台下亦不以公听之耶。言之者公。则虽终日陈之而不害于謇谔。听之者公。则虽终日闻之而不怒于烦苦。夫公者天下之直道也。且台下一日临此。名虽直指。而实则隐然字牧。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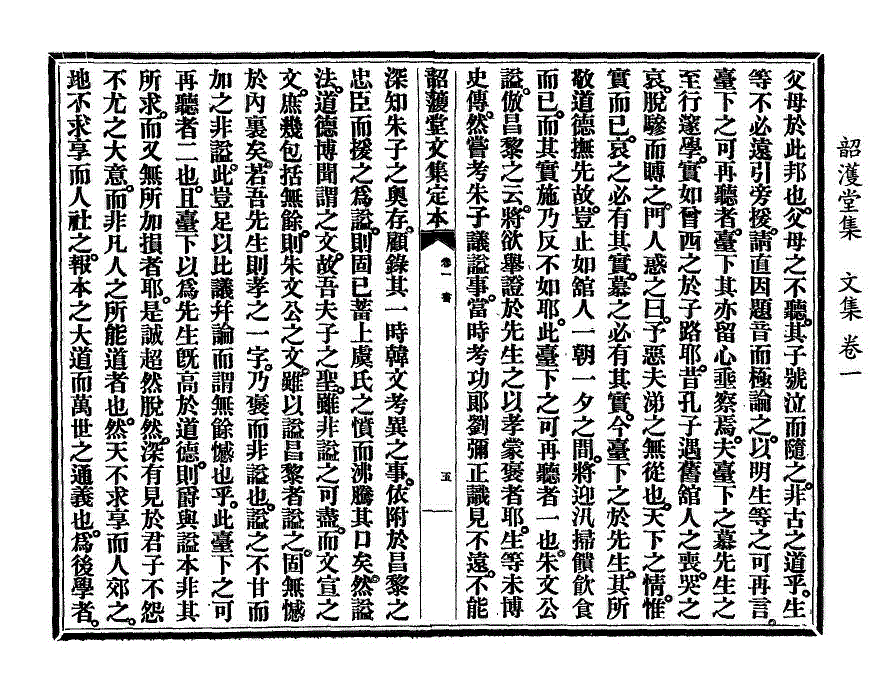 父母于此邦也。父母之不听。其子号泣而随之。非古之道乎。生等不必远引旁援。请直因题音而极论之。以明生等之可再言。台下之可再听者。台下其亦留心垂察焉。夫台下之慕先生之至行邃学。实如曾西之于子路耶。昔孔子遇旧馆人之丧。哭之哀。脱骖而赙之。门人惑之曰。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天下之情。惟实而已。哀之必有其实。慕之必有其实。今台下之于先生。其所敬道德抚先故。岂止如馆人一朝一夕之间。将迎汛扫馈饮食而已。而其实施乃反不如耶。此台下之可再听者一也。朱文公谥。仿昌黎之云。将欲举證于先生之以孝蒙褒者耶。生等未博史传。然尝考朱子议谥事。当时考功郎刘弥正识见不远。不能深知朱子之奥存。顾录其一时韩文考异之事。依附于昌黎之忠臣而援之为谥。则固已蓄上虞氏之愤而沸腾其口矣。然谥法。道德博闻谓之文。故吾夫子之圣。虽非谥之可尽。而文宣之文。庶几包括无馀。则朱文公之文。虽以谥昌黎者谥之。固无憾于内里矣。若吾先生则孝之一字。乃褒而非谥也。谥之不甘而加之非谥。此岂足以比议并论而谓无馀憾也乎。此台下之可再听者二也。且台下以为先生既高于道德。则爵与谥本非其所求。而又无所加损者耶。是诚超然脱然。深有见于君子不怨不尤之大意。而非凡人之所能道者也。然天不求享而人郊之。地不求享而人社之。报本之大道而万世之通义也。为后学者。
父母于此邦也。父母之不听。其子号泣而随之。非古之道乎。生等不必远引旁援。请直因题音而极论之。以明生等之可再言。台下之可再听者。台下其亦留心垂察焉。夫台下之慕先生之至行邃学。实如曾西之于子路耶。昔孔子遇旧馆人之丧。哭之哀。脱骖而赙之。门人惑之曰。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天下之情。惟实而已。哀之必有其实。慕之必有其实。今台下之于先生。其所敬道德抚先故。岂止如馆人一朝一夕之间。将迎汛扫馈饮食而已。而其实施乃反不如耶。此台下之可再听者一也。朱文公谥。仿昌黎之云。将欲举證于先生之以孝蒙褒者耶。生等未博史传。然尝考朱子议谥事。当时考功郎刘弥正识见不远。不能深知朱子之奥存。顾录其一时韩文考异之事。依附于昌黎之忠臣而援之为谥。则固已蓄上虞氏之愤而沸腾其口矣。然谥法。道德博闻谓之文。故吾夫子之圣。虽非谥之可尽。而文宣之文。庶几包括无馀。则朱文公之文。虽以谥昌黎者谥之。固无憾于内里矣。若吾先生则孝之一字。乃褒而非谥也。谥之不甘而加之非谥。此岂足以比议并论而谓无馀憾也乎。此台下之可再听者二也。且台下以为先生既高于道德。则爵与谥本非其所求。而又无所加损者耶。是诚超然脱然。深有见于君子不怨不尤之大意。而非凡人之所能道者也。然天不求享而人郊之。地不求享而人社之。报本之大道而万世之通义也。为后学者。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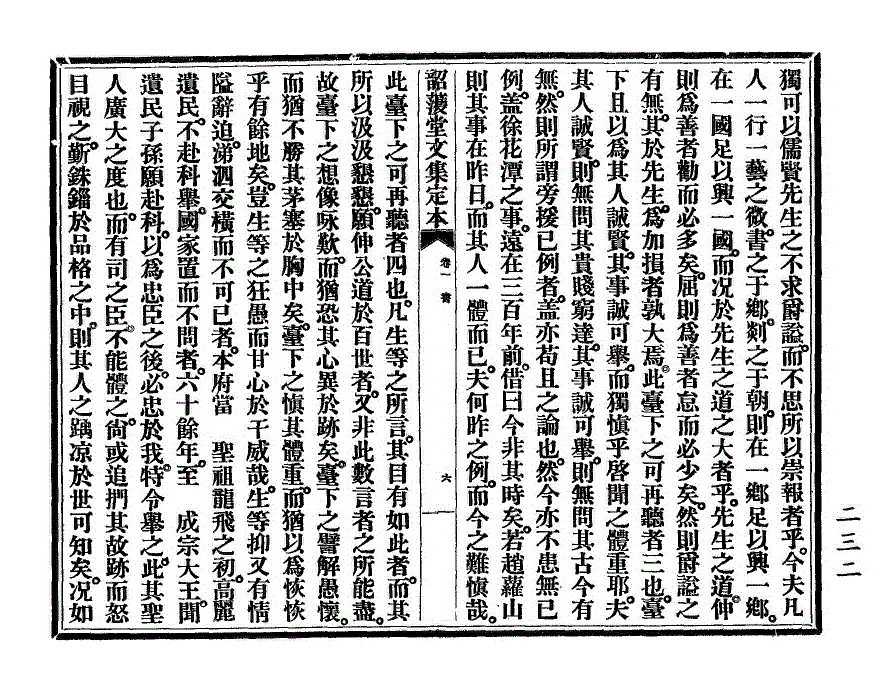 独可以儒贤先生之不求爵谥。而不思所以崇报者乎。今夫凡人一行一艺之微。书之于乡。剡之于朝。则在一乡足以兴一乡。在一国足以兴一国。而况于先生之道之大者乎。先生之道。伸则为善者劝而必多矣。屈则为善者怠而必少矣。然则爵谥之有无。其于先生。为加损者孰大焉。此台下之可再听者三也。台下且以为其人诚贤。其事诚可举。而独慎乎启闻之体重耶。夫其人诚贤。则无问其贵贱穷达。其事诚可举。则无问其古今有无。然则所谓旁援已例者。盖亦苟且之论也。然今亦不患无已例。盖徐花潭之事。远在三百年前。借曰今非其时矣。若赵萝山则其事在昨日。而其人一体而已。夫何昨之例。而今之难慎哉。此台下之可再听者四也。凡生等之所言。其目有如此者。而其所以汲汲恳恳。愿伸公道于百世者。又非此数言者之所能尽。故台下之想像咏叹。而犹恐其心异于迹矣。台下之譬解愚怀。而犹不胜其茅塞于胸中矣。台下之慎其体重。而犹以为恢恢乎有馀地矣。岂生等之狂愚而甘心于干威哉。生等抑又有情隘辞迫。涕泗交横而不可已者。本府当 圣祖龙飞之初。高丽遗民。不赴科举。国家置而不问者。六十馀年。至 成宗大王。闻遗民子孙愿赴科。以为忠臣之后。必忠于我。特令举之。此其圣人广大之度也。而有司之臣。不能体之。尚或追扪其故迹而怒目视之。芹铢锱于品格之中。则其人之踽凉于世可知矣。况如
独可以儒贤先生之不求爵谥。而不思所以崇报者乎。今夫凡人一行一艺之微。书之于乡。剡之于朝。则在一乡足以兴一乡。在一国足以兴一国。而况于先生之道之大者乎。先生之道。伸则为善者劝而必多矣。屈则为善者怠而必少矣。然则爵谥之有无。其于先生。为加损者孰大焉。此台下之可再听者三也。台下且以为其人诚贤。其事诚可举。而独慎乎启闻之体重耶。夫其人诚贤。则无问其贵贱穷达。其事诚可举。则无问其古今有无。然则所谓旁援已例者。盖亦苟且之论也。然今亦不患无已例。盖徐花潭之事。远在三百年前。借曰今非其时矣。若赵萝山则其事在昨日。而其人一体而已。夫何昨之例。而今之难慎哉。此台下之可再听者四也。凡生等之所言。其目有如此者。而其所以汲汲恳恳。愿伸公道于百世者。又非此数言者之所能尽。故台下之想像咏叹。而犹恐其心异于迹矣。台下之譬解愚怀。而犹不胜其茅塞于胸中矣。台下之慎其体重。而犹以为恢恢乎有馀地矣。岂生等之狂愚而甘心于干威哉。生等抑又有情隘辞迫。涕泗交横而不可已者。本府当 圣祖龙飞之初。高丽遗民。不赴科举。国家置而不问者。六十馀年。至 成宗大王。闻遗民子孙愿赴科。以为忠臣之后。必忠于我。特令举之。此其圣人广大之度也。而有司之臣。不能体之。尚或追扪其故迹而怒目视之。芹铢锱于品格之中。则其人之踽凉于世可知矣。况如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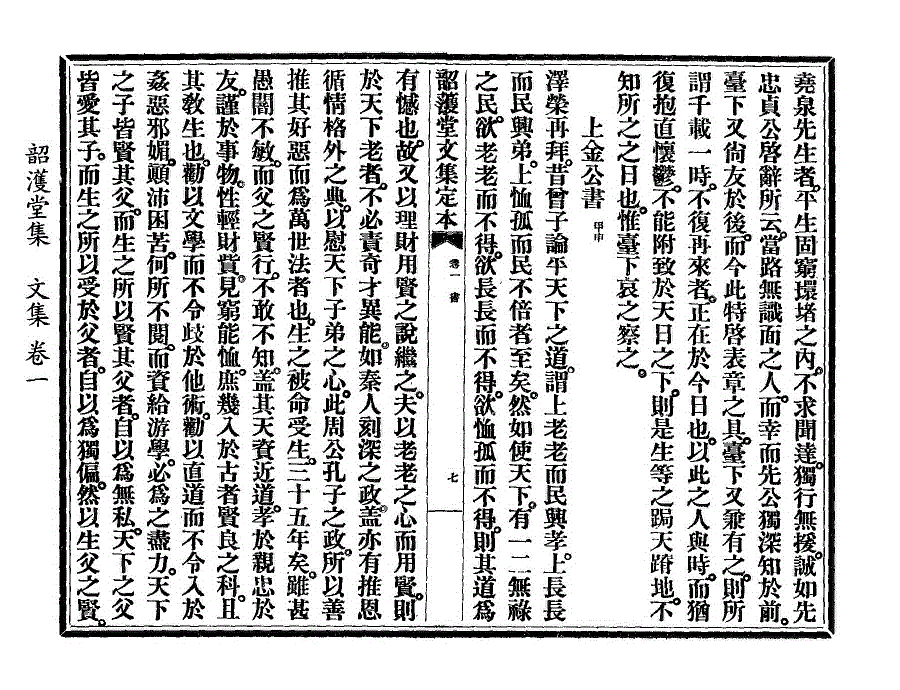 尧泉先生者。平生固穷环堵之内。不求闻达。独行无援。诚如先忠贞公启辞所云。当路无识面之人。而幸而先公独深知于前。台下又尚友于后。而今此特启表章之具。台下又兼有之。则所谓千载一时。不复再来者。正在于今日也。以此之人与时。而犹复抱直怀郁。不能附致于天日之下。则是生等之跼天蹐地。不知所之之日也。惟台下哀之察之。
尧泉先生者。平生固穷环堵之内。不求闻达。独行无援。诚如先忠贞公启辞所云。当路无识面之人。而幸而先公独深知于前。台下又尚友于后。而今此特启表章之具。台下又兼有之。则所谓千载一时。不复再来者。正在于今日也。以此之人与时。而犹复抱直怀郁。不能附致于天日之下。则是生等之跼天蹐地。不知所之之日也。惟台下哀之察之。上金公书(甲申)
泽荣再拜。昔曾子论平天下之道。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者至矣。然如使天下。有一二无禄之民。欲老老而不得。欲长长而不得。欲恤孤而不得。则其道为有憾也。故又以理财用贤之说继之。夫以老老之心而用贤。则于天下老者。不必责奇才异能。如秦人刻深之政。盖亦有推恩循情格外之典。以慰天下子弟之心。此周公孔子之政。所以善推其好恶而为万世法者也。生之被命受生。三十五年矣。虽甚愚闇不敏。而父之贤行。不敢不知。盖其天资近道。孝于亲忠于友。谨于事物。性轻财赀。见穷能恤。庶几入于古者贤良之科。且其教生也。劝以文学而不令歧于他术。劝以直道而不令入于奸恶邪媚。颠沛困苦。何所不阅。而资给游学。必为之尽力。天下之子皆贤其父。而生之所以贤其父者。自以为无私。天下之父皆爱其子。而生之所以受于父者。自以为独偏。然以生父之贤。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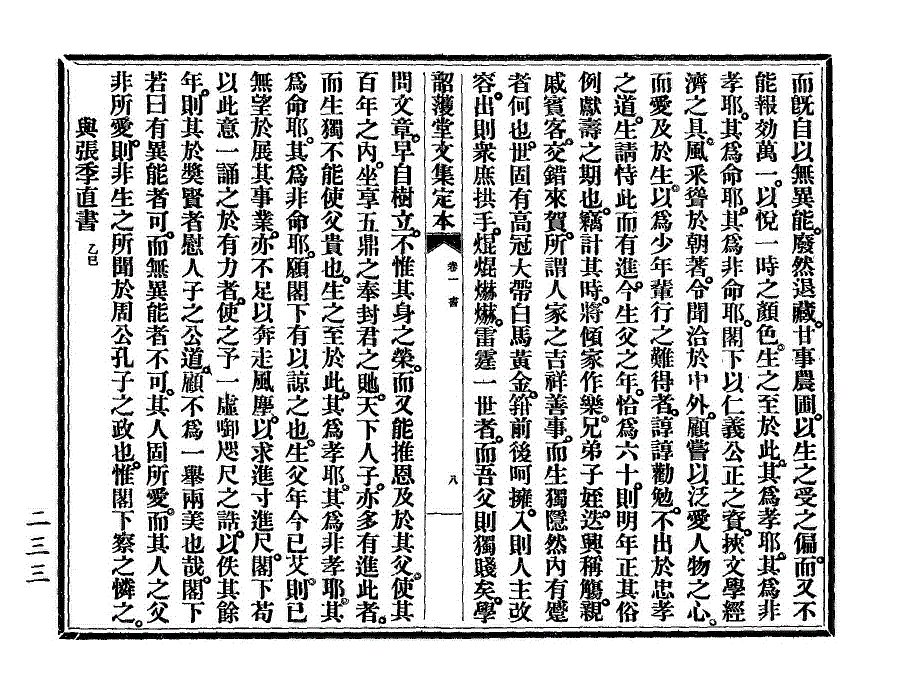 而既自以无异能。废然退藏。甘事农圃。以生之受之偏。而又不能报效万一。以悦一时之颜色。生之至于此。其为孝耶。其为非孝耶。其为命耶。其为非命耶。阁下以仁义公正之资。挟文学经济之具。风采耸于朝著。令闻洽于中外。顾尝以泛爱人物之心。而爱及于生。以为少年辈行之难得者。谆谆劝勉。不出于忠孝之道。生请恃此而有进。今生父之年。恰为六十。则明年正其俗例献寿之期也。窃计其时。将倾家作乐。兄弟子侄。迭兴称觞。亲戚宾客。交错来贺。所谓人家之吉祥善事。而生独隐然内有蹙者何也。世固有高冠大带白马黄金。钳前后呵拥。入则人主改容。出则众庶拱手。焜焜赫赫。雷霆一世者。而吾父则独贱矣。学问文章。早自树立。不惟其身之荣。而又能推恩及于其父。使其百年之内。坐享五鼎之奉封君之貤。天下人子。亦多有进此者。而生独不能使父贵也。生之至于此。其为孝耶。其为非孝耶。其为命耶。其为非命耶。愿阁下有以谅之也。生父年今已艾。则已无望于展其事业。亦不足以奔走风尘。以求进寸进尺。阁下苟以此意一诵之于有力者。使之予一虚衔咫尺之诰。以佚其馀年。则其于奖贤者慰人子之公道。顾不为一举两美也哉。阁下若曰有异能者可。而无异能者不可。其人固所爱。而其人之父非所爱。则非生之所闻于周公孔子之政也。惟阁下察之怜之。
而既自以无异能。废然退藏。甘事农圃。以生之受之偏。而又不能报效万一。以悦一时之颜色。生之至于此。其为孝耶。其为非孝耶。其为命耶。其为非命耶。阁下以仁义公正之资。挟文学经济之具。风采耸于朝著。令闻洽于中外。顾尝以泛爱人物之心。而爱及于生。以为少年辈行之难得者。谆谆劝勉。不出于忠孝之道。生请恃此而有进。今生父之年。恰为六十。则明年正其俗例献寿之期也。窃计其时。将倾家作乐。兄弟子侄。迭兴称觞。亲戚宾客。交错来贺。所谓人家之吉祥善事。而生独隐然内有蹙者何也。世固有高冠大带白马黄金。钳前后呵拥。入则人主改容。出则众庶拱手。焜焜赫赫。雷霆一世者。而吾父则独贱矣。学问文章。早自树立。不惟其身之荣。而又能推恩及于其父。使其百年之内。坐享五鼎之奉封君之貤。天下人子。亦多有进此者。而生独不能使父贵也。生之至于此。其为孝耶。其为非孝耶。其为命耶。其为非命耶。愿阁下有以谅之也。生父年今已艾。则已无望于展其事业。亦不足以奔走风尘。以求进寸进尺。阁下苟以此意一诵之于有力者。使之予一虚衔咫尺之诰。以佚其馀年。则其于奖贤者慰人子之公道。顾不为一举两美也哉。阁下若曰有异能者可。而无异能者不可。其人固所爱。而其人之父非所爱。则非生之所闻于周公孔子之政也。惟阁下察之怜之。与张季直书(乙巳)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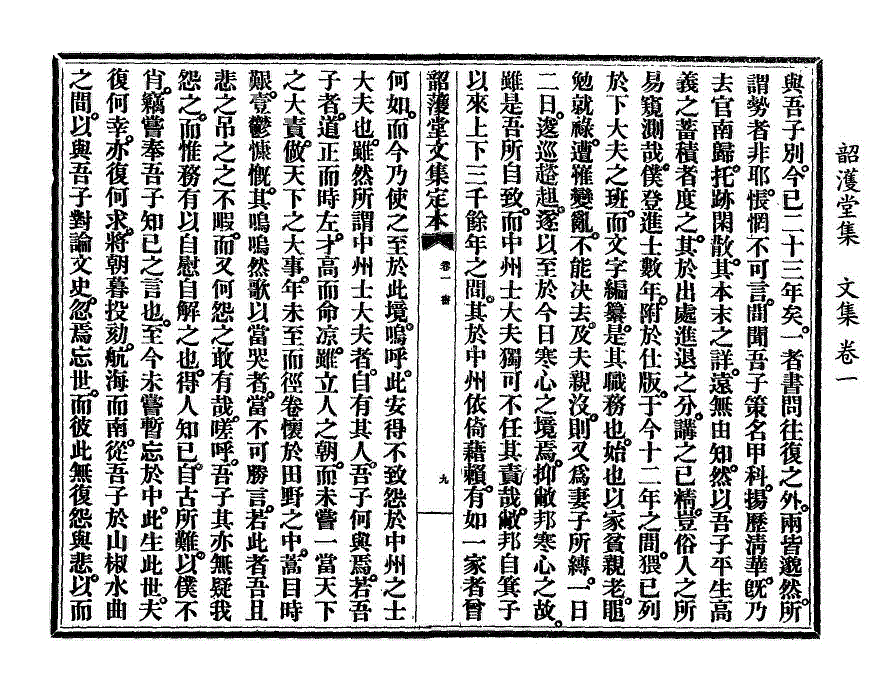 与吾子别。今已二十三年矣。一者书问往复之外。两皆邈然。所谓势者非耶。怅惘不可言。间闻吾子策名甲科。扬历清华。既乃去官南归。托迹闲散。其本末之详。远无由知。然以吾子平生高义之蓄积者度之。其于出处进退之分。讲之已精。岂俗人之所易窥测哉。仆登进士数年。附于仕版。于今十二年之间。猥已列于下大夫之班。而文字编纂。是其职务也。始也以家贫亲老。黾勉就禄。遭罹变乱。不能决去。及夫亲没。则又为妻子所缚。一日二日。逡巡趑趄。遂以至于今日寒心之境焉。抑敝邦寒心之故。虽是吾所自致。而中州士大夫独可不任其责哉。敝邦自箕子以来上下三千馀年之间。其于中州依倚藉赖。有如一家者曾何如。而今乃使之至于此境。呜呼。此安得不致怨于中州之士大夫也。虽然所谓中州士大夫者。自有其人。吾子何与焉。若吾子者。道正而时左。才高而命凉。虽立人之朝。而未尝一当天下之大责。做天下之大事。年未至而径卷怀于田野之中。蒿目时艰。壹郁慷慨。其呜呜然歌以当哭者。当不可胜言。若此者吾且悲之吊之之不暇。而又何怨之敢有哉。嗟呼。吾子其亦无疑我怨之。而惟务有以自慰自解之也。得人知己。自古所难。以仆不肖。窃尝奉吾子知己之言也。至今未尝暂忘于中。此生此世。夫复何幸。亦复何求。将朝暮投劾。航海而南。从吾子于山椒水曲之间。以与吾子对论文史。忽焉忘世。而彼此无复怨与悲。以而
与吾子别。今已二十三年矣。一者书问往复之外。两皆邈然。所谓势者非耶。怅惘不可言。间闻吾子策名甲科。扬历清华。既乃去官南归。托迹闲散。其本末之详。远无由知。然以吾子平生高义之蓄积者度之。其于出处进退之分。讲之已精。岂俗人之所易窥测哉。仆登进士数年。附于仕版。于今十二年之间。猥已列于下大夫之班。而文字编纂。是其职务也。始也以家贫亲老。黾勉就禄。遭罹变乱。不能决去。及夫亲没。则又为妻子所缚。一日二日。逡巡趑趄。遂以至于今日寒心之境焉。抑敝邦寒心之故。虽是吾所自致。而中州士大夫独可不任其责哉。敝邦自箕子以来上下三千馀年之间。其于中州依倚藉赖。有如一家者曾何如。而今乃使之至于此境。呜呼。此安得不致怨于中州之士大夫也。虽然所谓中州士大夫者。自有其人。吾子何与焉。若吾子者。道正而时左。才高而命凉。虽立人之朝。而未尝一当天下之大责。做天下之大事。年未至而径卷怀于田野之中。蒿目时艰。壹郁慷慨。其呜呜然歌以当哭者。当不可胜言。若此者吾且悲之吊之之不暇。而又何怨之敢有哉。嗟呼。吾子其亦无疑我怨之。而惟务有以自慰自解之也。得人知己。自古所难。以仆不肖。窃尝奉吾子知己之言也。至今未尝暂忘于中。此生此世。夫复何幸。亦复何求。将朝暮投劾。航海而南。从吾子于山椒水曲之间。以与吾子对论文史。忽焉忘世。而彼此无复怨与悲。以而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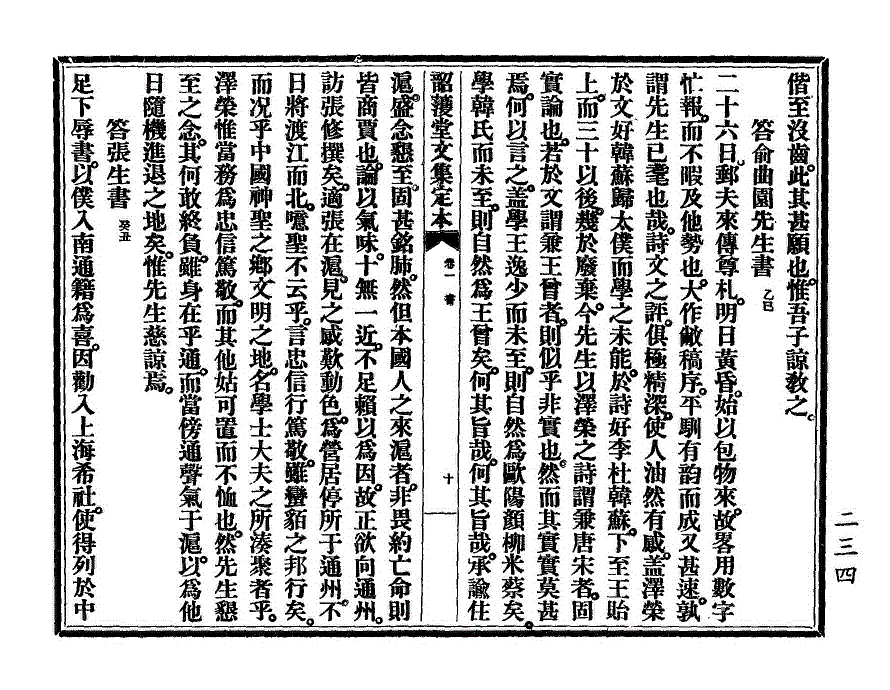 偕至没齿。此其甚愿也。惟吾子谅教之。
偕至没齿。此其甚愿也。惟吾子谅教之。答俞曲园先生书(乙巳)
二十六日。邮夫来传尊札。明日黄昏。始以包物来。故略用数字忙报。而不暇及他势也。大作敝稿序。平驯有韵而成又甚速。孰谓先生已耄也哉。诗文之评。俱极精深。使人油然有感。盖泽荣于文好韩苏归太仆而学之未能。于诗好李杜韩苏。下至王贻上。而三十以后。几于废弃。今先生以泽荣之诗谓兼唐宋者。固实论也。若于文谓兼王曾者。则似乎非实也。然而其实实莫甚焉。何以言之。盖学王逸少而未至。则自然为欧阳颜柳米蔡矣。学韩氏而未至。则自然为王曾矣。何其旨哉。何其旨哉。承谕住沪。盛念恳至。固甚铭肺。然但本国人之来沪者。非畏约亡命则皆商贾也。论以气味。十无一近。不足赖以为因。故正欲向通州。访张修撰矣。适张在沪。见之感叹动色。为营居停所于通州。不日将渡江而北。噫圣不云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而况乎中国神圣之乡文明之地。名学士大夫之所凑聚者乎。泽荣惟当务为忠信笃敬。而其他姑可置而不恤也。然先生恳至之念。其何敢终负。虽身在乎通。而当傍通声气于沪。以为他日随机进退之地矣。惟先生慈谅焉。
答张生书(癸丑)
足下辱书。以仆入南通籍为喜。因劝入上海希社。使得列于中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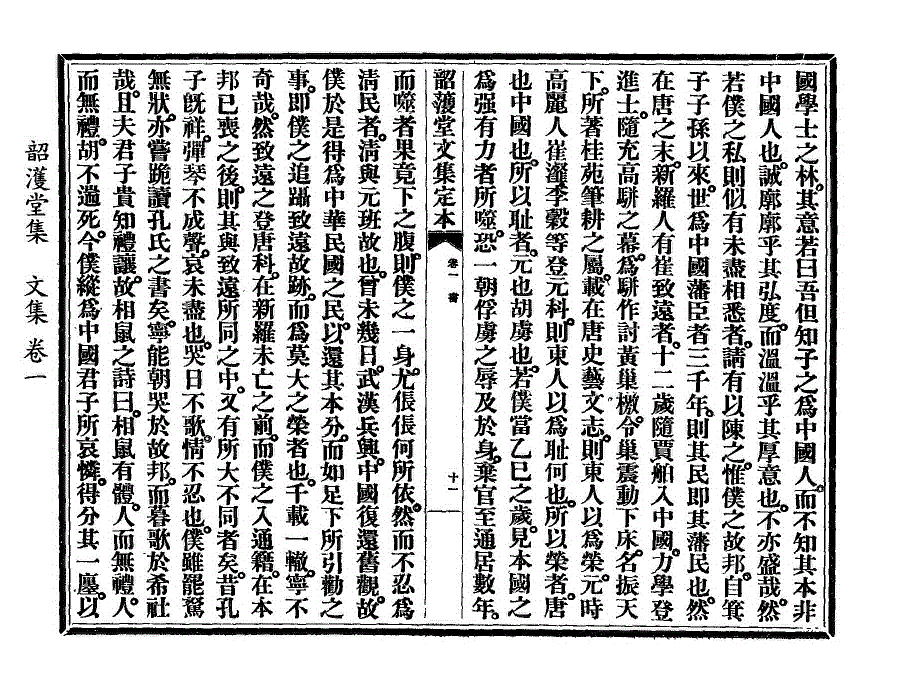 国学士之林。其意若曰吾但知子之为中国人。而不知其本非中国人也。诚廓廓乎其弘度。而温温乎其厚意也。不亦盛哉。然若仆之私则似有未尽相悉者。请有以陈之。惟仆之故邦。自箕子子孙以来。世为中国藩臣者三千年。则其民即其藩民也。然在唐之末。新罗人有崔致远者。十二岁随贾舶入中国。力学登进士。随充高骈之幕。为骈作讨黄巢檄。令巢震动下床。名振天下。所著桂苑笔耕之属。载在唐史艺文志。则东人以为荣。元时高丽人崔瀣,李谷等登元科。则东人以为耻何也。所以荣者。唐也中国也。所以耻者。元也胡虏也。若仆当乙巳之岁。见本国之为强有力者所噬。恐一朝俘虏之辱及于身。弃官至通居数年。而噬者果竟下之腹。则仆之一身。尤伥伥何所依。然而不忍为清民者。清与元班故也。曾未几日。武汉兵兴。中国复还旧观。故仆于是得为中华民国之民。以还其本分。而如足下所引劝之事。即仆之追蹑致远故迹。而为莫大之荣者也。千载一辙。宁不奇哉。然致远之登唐科。在新罗未亡之前。而仆之入通籍。在本邦已丧之后。则其与致远所同之中。又有所大不同者矣。昔孔子既祥。弹琴不成声。哀未尽也。哭日不歌。情不忍也。仆虽罢驽无状。亦尝跪读孔氏之书矣。宁能朝哭于故邦。而暮歌于希社哉。且夫君子贵知礼让。故相鼠之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今仆纵为中国君子所哀怜。得分其一廛。以
国学士之林。其意若曰吾但知子之为中国人。而不知其本非中国人也。诚廓廓乎其弘度。而温温乎其厚意也。不亦盛哉。然若仆之私则似有未尽相悉者。请有以陈之。惟仆之故邦。自箕子子孙以来。世为中国藩臣者三千年。则其民即其藩民也。然在唐之末。新罗人有崔致远者。十二岁随贾舶入中国。力学登进士。随充高骈之幕。为骈作讨黄巢檄。令巢震动下床。名振天下。所著桂苑笔耕之属。载在唐史艺文志。则东人以为荣。元时高丽人崔瀣,李谷等登元科。则东人以为耻何也。所以荣者。唐也中国也。所以耻者。元也胡虏也。若仆当乙巳之岁。见本国之为强有力者所噬。恐一朝俘虏之辱及于身。弃官至通居数年。而噬者果竟下之腹。则仆之一身。尤伥伥何所依。然而不忍为清民者。清与元班故也。曾未几日。武汉兵兴。中国复还旧观。故仆于是得为中华民国之民。以还其本分。而如足下所引劝之事。即仆之追蹑致远故迹。而为莫大之荣者也。千载一辙。宁不奇哉。然致远之登唐科。在新罗未亡之前。而仆之入通籍。在本邦已丧之后。则其与致远所同之中。又有所大不同者矣。昔孔子既祥。弹琴不成声。哀未尽也。哭日不歌。情不忍也。仆虽罢驽无状。亦尝跪读孔氏之书矣。宁能朝哭于故邦。而暮歌于希社哉。且夫君子贵知礼让。故相鼠之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今仆纵为中国君子所哀怜。得分其一廛。以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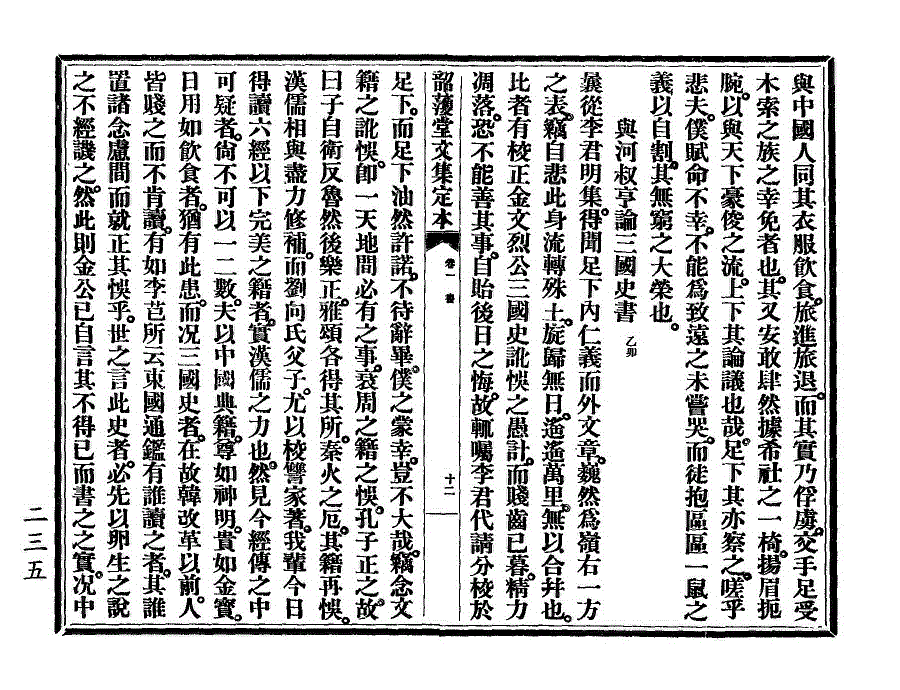 与中国人同其衣服饮食。旅进旅退。而其实乃俘虏。交手足受木索之族之幸免者也。其又安敢肆然据希社之一椅。扬眉扼腕。以与天下豪俊之流。上下其论议也哉。足下其亦察之。嗟乎悲夫。仆赋命不幸。不能为致远之未尝哭。而徒抱区区一鼠之义以自割。其无穷之大荣也。
与中国人同其衣服饮食。旅进旅退。而其实乃俘虏。交手足受木索之族之幸免者也。其又安敢肆然据希社之一椅。扬眉扼腕。以与天下豪俊之流。上下其论议也哉。足下其亦察之。嗟乎悲夫。仆赋命不幸。不能为致远之未尝哭。而徒抱区区一鼠之义以自割。其无穷之大荣也。与河叔亨论三国史书(乙卯)
曩从李君明集。得闻足下内仁义而外文章。巍然为岭右一方之表。窃自悲此身流转殊土。旋归无日。遥遥万里。无以合并也。比者有校正金文烈公三国史讹误之愚计。而贱齿已暮。精力凋落。恐不能善其事。自贻后日之悔。故辄嘱李君代请分校于足下。而足下油然许诺。不待辞毕。仆之蒙幸。岂不大哉。窃念文籍之讹误。即一天地间必有之事。衰周之籍之误。孔子正之。故曰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秦火之厄。其籍再误。汉儒相与尽力修补。而刘向氏父子。尤以校雠家著。我辈今日得读六经以下完美之籍者。实汉儒之力也。然见今经传之中可疑者。尚不可以一二数。夫以中国典籍。尊如神明。贵如金宝。日用如饮食者。犹有此患。而况三国史者。在故韩改革以前。人皆贱之而不肯读。有如李芑所云东国通鉴有谁读之者。其谁置诸念虑间而就正其误乎。世之言此史者。必先以卵生之说之不经讥之。然此则金公已自言其不得已而书之之实。况中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6H 页
 国古史。亦有人身牛首玄鸟堕卵等文。此则置之勿论可也。只就其可修者而言之。新罗始祖纪曰。五年春正月。龙见于阏英井。右胁诞生女儿。老妪见而异之收养之。以井名名之。及长有德容。始祖闻之。纳以为妃。苟如此文。则阏英以春正月生。其年为始祖妃。有是理哉。此可以知春正月之下。亡去纳阏英为妃先是七字也断然矣。花郎事及强首传。杂志等所引书名。即是傍注误入正文者也。其外可疑者亦复不少。岂以金公典茂近古之文章。度越郑麟趾辈数倍者。而污至于此也。意者其初稿之荒乱者行于世耶。不然则刊行之际。抄写有误耶。目今故邦之寒心甚矣。遗黎之可以寄想于旧物者。惟有书籍而已。况是史为其最首出之正史。其所贵重。犹之伏羲之八卦夏禹之九鼎。则我辈其可不戮力修正。一以伸金公之幽冤。一以增遗黎之寄想也哉。仆既已幸承分校之德意。然文字之道。贵在讲论相资。故不惮烦琐。陈之如右。足下将何以回示德音而玉我也耶。
国古史。亦有人身牛首玄鸟堕卵等文。此则置之勿论可也。只就其可修者而言之。新罗始祖纪曰。五年春正月。龙见于阏英井。右胁诞生女儿。老妪见而异之收养之。以井名名之。及长有德容。始祖闻之。纳以为妃。苟如此文。则阏英以春正月生。其年为始祖妃。有是理哉。此可以知春正月之下。亡去纳阏英为妃先是七字也断然矣。花郎事及强首传。杂志等所引书名。即是傍注误入正文者也。其外可疑者亦复不少。岂以金公典茂近古之文章。度越郑麟趾辈数倍者。而污至于此也。意者其初稿之荒乱者行于世耶。不然则刊行之际。抄写有误耶。目今故邦之寒心甚矣。遗黎之可以寄想于旧物者。惟有书籍而已。况是史为其最首出之正史。其所贵重。犹之伏羲之八卦夏禹之九鼎。则我辈其可不戮力修正。一以伸金公之幽冤。一以增遗黎之寄想也哉。仆既已幸承分校之德意。然文字之道。贵在讲论相资。故不惮烦琐。陈之如右。足下将何以回示德音而玉我也耶。答人论古文书(丙辰)
自识足下以来。知足下好文有至心。兹者又辱致所著文。而请详示为文之法。其辞甚恭。其意甚勤。此仆生平所不几遇者也。虽仆之知识不逮古人。而重以衰昏。其何敢不竭其愚以奉助一二乎。盖凡曰理曰气曰心曰性。圣人未尝言之于道。而后世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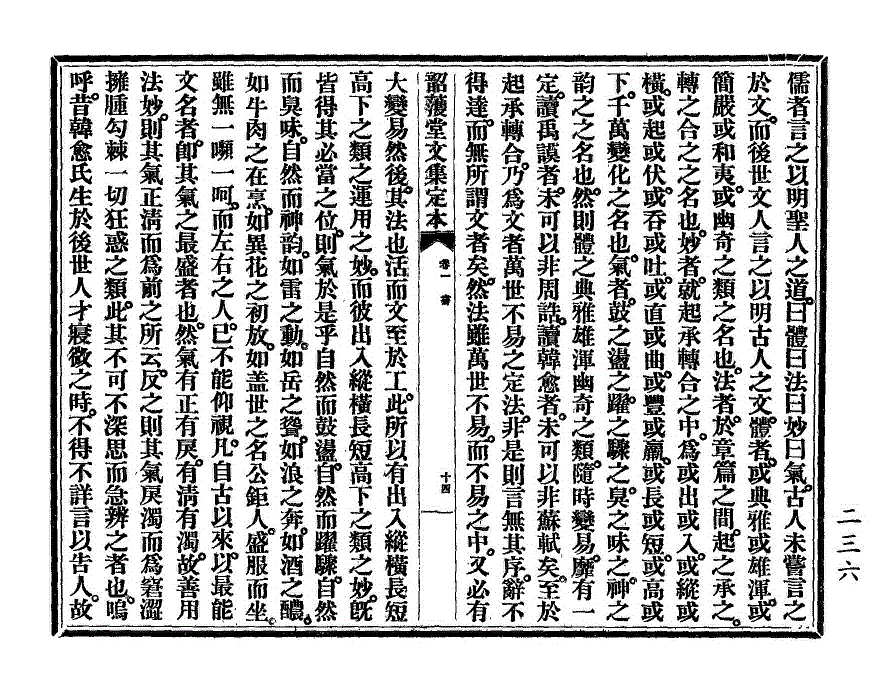 儒者言之以明圣人之道。曰体曰法曰妙曰气。古人未尝言之于文。而后世文人言之以明古人之文。体者。或典雅或雄浑。或简严或和夷。或幽奇之类之名也。法者。于章篇之间。起之承之。转之合之之名也。妙者。就起承转合之中。为或出或入。或纵或横。或起或伏。或吞或吐。或直或曲。或丰或羸。或长或短。或高或下。千万变化之名也。气者鼓之荡之。跃之骤之。臭之味之。神之韵之之名也。然则体之典雅雄浑幽奇之类。随时变易。靡有一定。读禹谟者。未可以非周诰。读韩愈者。未可以非苏轼矣。至于起承转合。乃为文者万世不易之定法。非是则言无其序。辞不得达。而无所谓文者矣。然法虽万世不易。而不易之中。又必有大变易然后。其法也活而文至于工。此所以有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运用之妙。而彼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妙。既皆得其必当之位。则气于是乎自然而鼓荡。自然而跃骤。自然而臭味。自然而神韵。如雷之动。如岳之耸。如浪之奔。如酒之醲。如牛肉之在烹。如异花之初放。如盖世之名公钜人。盛服而坐。虽无一嚬一呵。而左右之人。已不能仰视。凡自古以来。以最能文名者。即其气之最盛者也。然气有正有戾。有清有浊。故善用法妙。则其气正清而为前之所云。反之则其气戾浊而为窘涩拥肿勾棘一切狂惑之类。此其不可不深思而急辨之者也。呜呼。昔韩愈氏生于后世人才寝微之时。不得不详言以告人。故
儒者言之以明圣人之道。曰体曰法曰妙曰气。古人未尝言之于文。而后世文人言之以明古人之文。体者。或典雅或雄浑。或简严或和夷。或幽奇之类之名也。法者。于章篇之间。起之承之。转之合之之名也。妙者。就起承转合之中。为或出或入。或纵或横。或起或伏。或吞或吐。或直或曲。或丰或羸。或长或短。或高或下。千万变化之名也。气者鼓之荡之。跃之骤之。臭之味之。神之韵之之名也。然则体之典雅雄浑幽奇之类。随时变易。靡有一定。读禹谟者。未可以非周诰。读韩愈者。未可以非苏轼矣。至于起承转合。乃为文者万世不易之定法。非是则言无其序。辞不得达。而无所谓文者矣。然法虽万世不易。而不易之中。又必有大变易然后。其法也活而文至于工。此所以有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运用之妙。而彼出入纵横长短高下之类之妙。既皆得其必当之位。则气于是乎自然而鼓荡。自然而跃骤。自然而臭味。自然而神韵。如雷之动。如岳之耸。如浪之奔。如酒之醲。如牛肉之在烹。如异花之初放。如盖世之名公钜人。盛服而坐。虽无一嚬一呵。而左右之人。已不能仰视。凡自古以来。以最能文名者。即其气之最盛者也。然气有正有戾。有清有浊。故善用法妙。则其气正清而为前之所云。反之则其气戾浊而为窘涩拥肿勾棘一切狂惑之类。此其不可不深思而急辨之者也。呜呼。昔韩愈氏生于后世人才寝微之时。不得不详言以告人。故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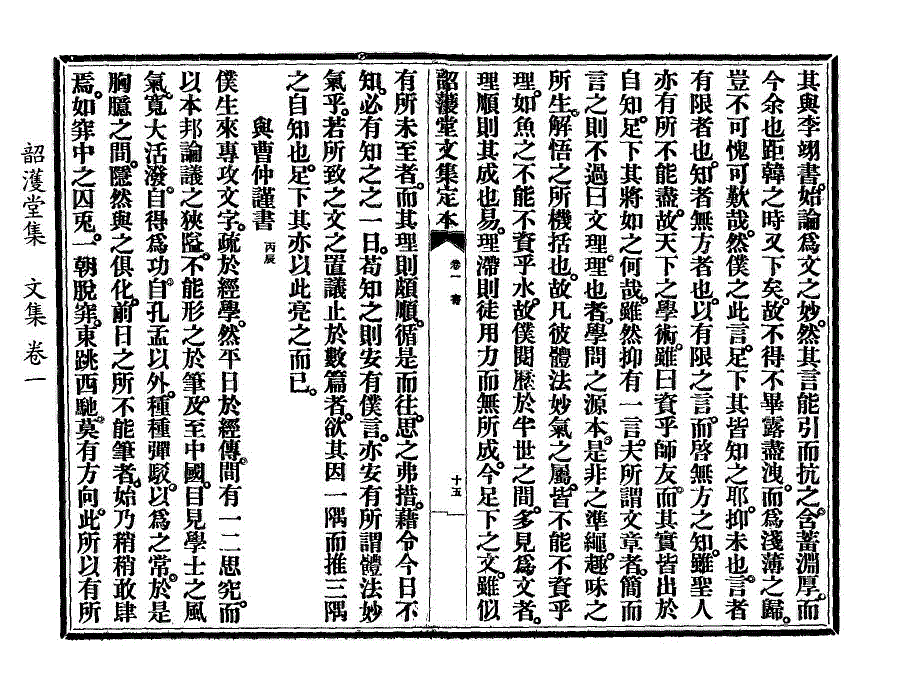 其与李翊书。始论为文之妙。然其言能引而抗之。含蓄渊厚。而今余也距韩之时又下矣。故不得不毕露尽泄。而为浅薄之归。岂不可愧可叹哉。然仆之此言。足下其皆知之耶。抑未也。言者有限者也。知者无方者也。以有限之言。而启无方之知。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故天下之学术。虽曰资乎师友。而其实皆出于自知。足下其将如之何哉。虽然抑有一言。夫所谓文章者。简而言之则不过曰文理。理也者。学问之源本。是非之准绳。趣味之所生。解悟之所机括也。故凡彼体法妙气之属。皆不能不资乎理。如鱼之不能不资乎水。故仆阅历于半世之间。多见为文者。理顺则其成也易。理滞则徒用力而无所成。今足下之文。虽似有所未至者。而其理则颇顺。循是而往。思之弗措。藉令今日不知。必有知之之一日。苟知之则安有仆言。亦安有所谓体法妙气乎。若所致之文之置议止于数篇者。欲其因一隅而推三隅之自知也。足下其亦以此亮之而已。
其与李翊书。始论为文之妙。然其言能引而抗之。含蓄渊厚。而今余也距韩之时又下矣。故不得不毕露尽泄。而为浅薄之归。岂不可愧可叹哉。然仆之此言。足下其皆知之耶。抑未也。言者有限者也。知者无方者也。以有限之言。而启无方之知。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故天下之学术。虽曰资乎师友。而其实皆出于自知。足下其将如之何哉。虽然抑有一言。夫所谓文章者。简而言之则不过曰文理。理也者。学问之源本。是非之准绳。趣味之所生。解悟之所机括也。故凡彼体法妙气之属。皆不能不资乎理。如鱼之不能不资乎水。故仆阅历于半世之间。多见为文者。理顺则其成也易。理滞则徒用力而无所成。今足下之文。虽似有所未至者。而其理则颇顺。循是而往。思之弗措。藉令今日不知。必有知之之一日。苟知之则安有仆言。亦安有所谓体法妙气乎。若所致之文之置议止于数篇者。欲其因一隅而推三隅之自知也。足下其亦以此亮之而已。与曹仲谨书(丙辰)
仆生来专攻文字。疏于经学。然平日于经传。间有一二思究。而以本邦论议之狭隘。不能形之于笔。及至中国。目见学士之风气。宽大活泼。自得为功。自孔孟以外。种种弹驳。以为之常。于是胸臆之间。隐然与之俱化。前日之所不能笔者。始乃稍稍敢肆焉。如阱中之囚兔。一朝脱阱。东跳西驰。莫有方向。此所以有所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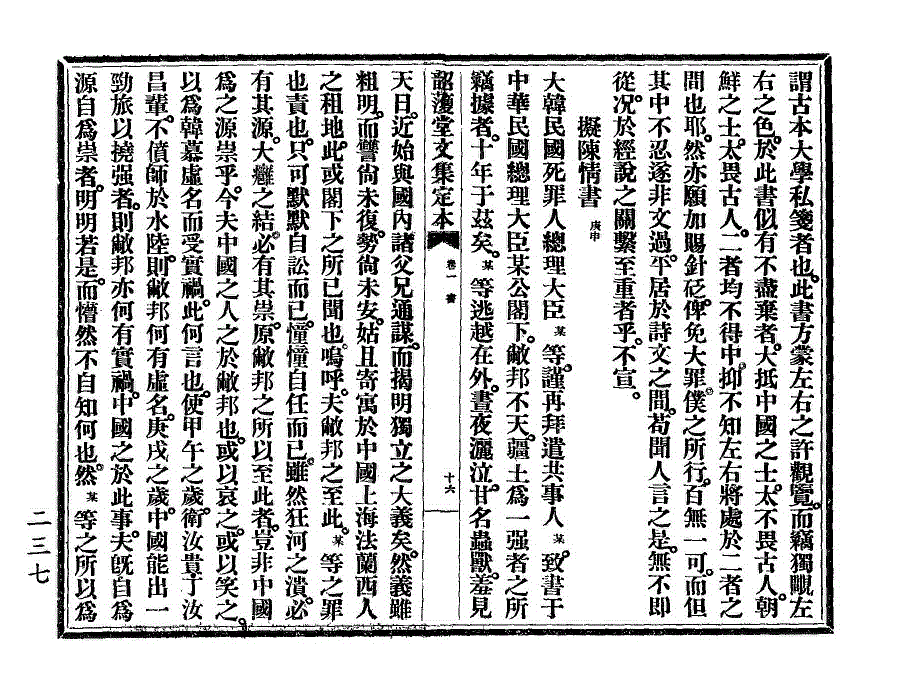 谓古本大学私笺者也。此书方蒙左右之许观览。而窃独覸左右之色。于此书似有不尽弃者。大抵中国之士。太不畏古人。朝鲜之士。太畏古人。二者均不得中。抑不知左右将处于二者之间也耶。然亦愿加赐针砭。俾免大罪。仆之所行。百无一可。而但其中不忍遂非文过。平居于诗文之间。苟闻人言之是。无不即从。况于经说之关系至重者乎。不宣。
谓古本大学私笺者也。此书方蒙左右之许观览。而窃独覸左右之色。于此书似有不尽弃者。大抵中国之士。太不畏古人。朝鲜之士。太畏古人。二者均不得中。抑不知左右将处于二者之间也耶。然亦愿加赐针砭。俾免大罪。仆之所行。百无一可。而但其中不忍遂非文过。平居于诗文之间。苟闻人言之是。无不即从。况于经说之关系至重者乎。不宣。拟陈情书(庚申)
大韩民国死罪人总理大臣某等。谨再拜遣共事人某。致书于中华民国总理大臣某公阁下。敝邦不天。疆土为一强者之所窃据者。十年于兹矣。某等逃越在外。昼夜洒泣。甘名虫兽。羞见天日。近始与国内诸父兄通谋。而揭明独立之大义矣。然义虽粗明。而雠尚未复。势尚未安。姑且寄寓于中国上海法兰西人之租地。此或阁下之所已闻也。呜呼。夫敝邦之至此。某等之罪也责也。只可默默自讼而已。憧憧自任而已。虽然狂河之溃。必有其源。大痈之结。必有其祟。原敝邦之所以至此者。岂非中国为之源祟乎。今夫中国之人之于敝邦也。或以哀之。或以笑之。以为韩慕虚名而受实祸。此何言也。使甲午之岁。卫汝贵,丁汝昌辈。不偾师于水陆。则敝邦何有虚名。庚戌之岁。中国能出一劲旅以挠强者。则敝邦亦何有实祸。中国之于此事。夫既自为源自为祟者。明明若是。而懵然不自知何也。然某等之所以为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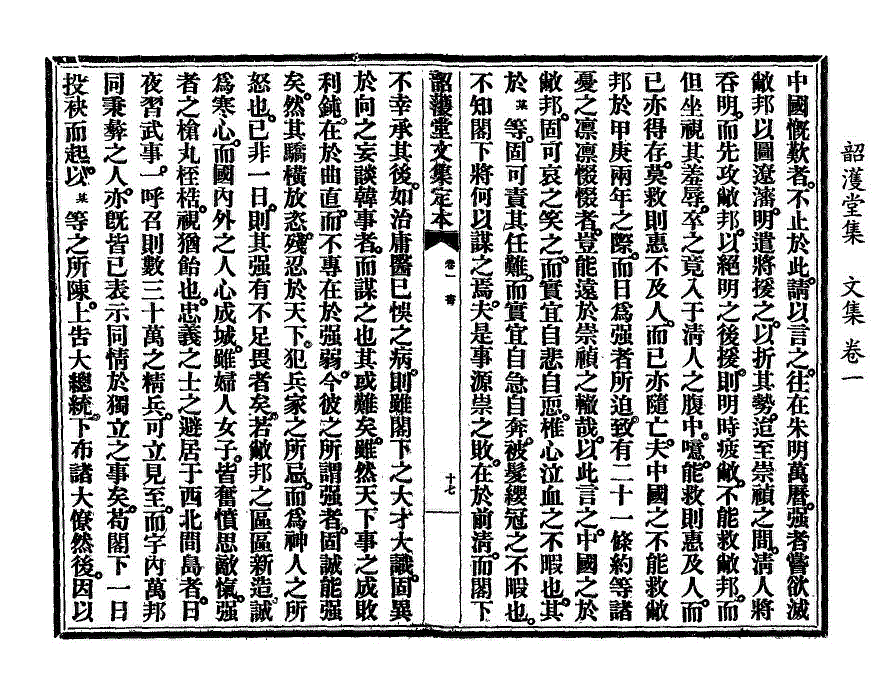 中国慨叹者。不止于此。请以言之。往在朱明万历。强者尝欲灭敝邦以图辽沈。明遣将援之。以折其势。迨至崇祯之间。清人将吞明。而先攻敝邦。以绝明之后援。则明时疲敝。不能救敝邦。而但坐视其羞辱。卒之竟入于清人之腹中。噫。能救则惠及人。而已亦得存。莫救则惠不及人。而已亦随亡。夫中国之不能救敝邦于甲庚两年之际。而日为强者所迫。致有二十一条约等诸忧之凛凛惙惙者。岂能远于崇祯之辙哉。以此言之。中国之于敝邦。固可哀之笑之。而实宜自悲自恧。椎心泣血之不暇也。其于某等。固可责其任难。而实宜自急自奔。被发缨冠之不暇也。不知阁下将何以谋之焉。夫是事源祟之败。在于前清。而阁下不幸承其后。如治庸医已误之病。则虽阁下之大才大识。固异于向之妄谈韩事者。而谋之也其或难矣。虽然天下事之成败利钝。在于曲直。而不专在于强弱。今彼之所谓强者。固诚能强矣。然其骄横放恣。残忍于天下。犯兵家之所忌。而为神人之所怒也。已非一日。则其强有不足畏者矣。若敝邦之区区新造。诚为寒心。而国内外之人心成城。虽妇人女子。皆奋愤思敌忾。强者之枪丸桎梏。视犹饴也。忠义之士之避居于西北间岛者。日夜习武事。一呼召则数三十万之精兵。可立见至。而宇内万邦同秉彝之人。亦既皆已表示同情于独立之事矣。苟阁下一日投袂而起。以某等之所陈。上告大总统。下布诸大僚然后。因以
中国慨叹者。不止于此。请以言之。往在朱明万历。强者尝欲灭敝邦以图辽沈。明遣将援之。以折其势。迨至崇祯之间。清人将吞明。而先攻敝邦。以绝明之后援。则明时疲敝。不能救敝邦。而但坐视其羞辱。卒之竟入于清人之腹中。噫。能救则惠及人。而已亦得存。莫救则惠不及人。而已亦随亡。夫中国之不能救敝邦于甲庚两年之际。而日为强者所迫。致有二十一条约等诸忧之凛凛惙惙者。岂能远于崇祯之辙哉。以此言之。中国之于敝邦。固可哀之笑之。而实宜自悲自恧。椎心泣血之不暇也。其于某等。固可责其任难。而实宜自急自奔。被发缨冠之不暇也。不知阁下将何以谋之焉。夫是事源祟之败。在于前清。而阁下不幸承其后。如治庸医已误之病。则虽阁下之大才大识。固异于向之妄谈韩事者。而谋之也其或难矣。虽然天下事之成败利钝。在于曲直。而不专在于强弱。今彼之所谓强者。固诚能强矣。然其骄横放恣。残忍于天下。犯兵家之所忌。而为神人之所怒也。已非一日。则其强有不足畏者矣。若敝邦之区区新造。诚为寒心。而国内外之人心成城。虽妇人女子。皆奋愤思敌忾。强者之枪丸桎梏。视犹饴也。忠义之士之避居于西北间岛者。日夜习武事。一呼召则数三十万之精兵。可立见至。而宇内万邦同秉彝之人。亦既皆已表示同情于独立之事矣。苟阁下一日投袂而起。以某等之所陈。上告大总统。下布诸大僚然后。因以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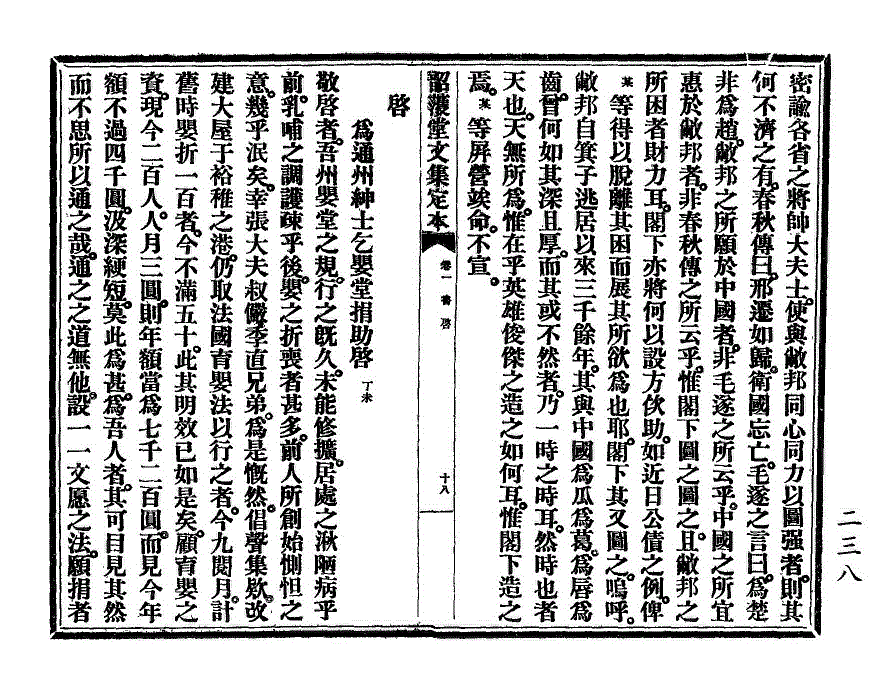 密谕各省之将帅大夫士。使与敝邦同心同力以图强者。则其何不济之有。春秋传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毛遂之言曰。为楚非为赵。敝邦之所愿于中国者。非毛遂之所云乎。中国之所宜惠于敝邦者。非春秋传之所云乎。惟阁下图之图之。且敝邦之所困者财力耳。阁下亦将何以设方佽助。如近日公债之例。俾某等得以脱离其困而展其所欲为也耶。阁下其又图之。呜呼。敝邦自箕子逃居以来三千馀年。其与中国为瓜为葛。为唇为齿。曾何如其深且厚。而其或不然者。乃一时之时耳。然时也者天也。天无所为。惟在乎英雄俊杰之造之如何耳。惟阁下造之焉。某等屏营俟命。不宣。
密谕各省之将帅大夫士。使与敝邦同心同力以图强者。则其何不济之有。春秋传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毛遂之言曰。为楚非为赵。敝邦之所愿于中国者。非毛遂之所云乎。中国之所宜惠于敝邦者。非春秋传之所云乎。惟阁下图之图之。且敝邦之所困者财力耳。阁下亦将何以设方佽助。如近日公债之例。俾某等得以脱离其困而展其所欲为也耶。阁下其又图之。呜呼。敝邦自箕子逃居以来三千馀年。其与中国为瓜为葛。为唇为齿。曾何如其深且厚。而其或不然者。乃一时之时耳。然时也者天也。天无所为。惟在乎英雄俊杰之造之如何耳。惟阁下造之焉。某等屏营俟命。不宣。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启
为通州绅士乞婴堂捐助启(丁未)
敬启者。吾州婴堂之规。行之既久。未能修扩。居处之湫陋病乎前。乳哺之调护疏乎后。婴之折丧者甚多。前人所创始恻怛之意。几乎泯矣。幸张大夫叔俨,季直兄弟。为是慨然。倡声集款。改建大屋于裕稚之港。仍取法国育婴法以行之者。今九阅月。计旧时婴折一百者。今不满五十。此其明效已如是矣。顾育婴之资。现今二百人。人月三圆。则年额当为七千二百圆。而见今年额不过四千圆。汲深绠短。莫此为甚。为吾人者。其可目见其然而不思所以通之哉。通之之道无他。设一一文愿之法。愿捐者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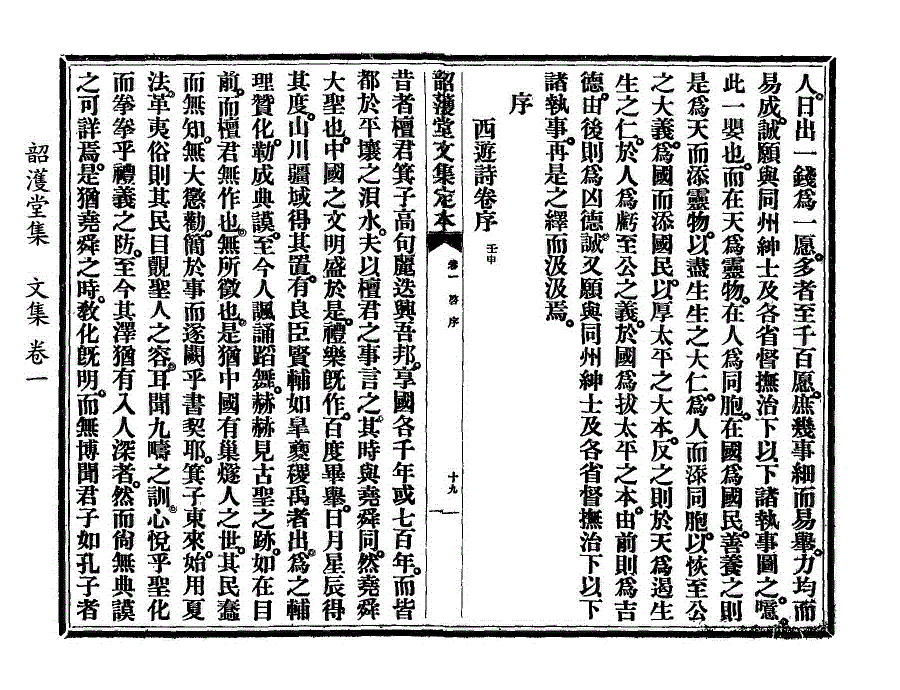 人。日出一钱为一愿。多者至千百愿。庶几事细而易举。力均而易成。诚愿与同州绅士及各省督抚治下以下诸执事图之。噫。此一婴也。而在天为灵物。在人为同胞。在国为国民。善养之则是为天而添灵物。以尽生生之大仁。为人而添同胞。以恢至公之大义。为国而添国民。以厚太平之大本。反之则于天为遏生生之仁。于人为亏至公之义。于国为拔太平之本。由前则为吉德。由后则为凶德。诚又愿与同州绅士及各省督抚治下以下诸执事。再是之绎而汲汲焉。
人。日出一钱为一愿。多者至千百愿。庶几事细而易举。力均而易成。诚愿与同州绅士及各省督抚治下以下诸执事图之。噫。此一婴也。而在天为灵物。在人为同胞。在国为国民。善养之则是为天而添灵物。以尽生生之大仁。为人而添同胞。以恢至公之大义。为国而添国民。以厚太平之大本。反之则于天为遏生生之仁。于人为亏至公之义。于国为拔太平之本。由前则为吉德。由后则为凶德。诚又愿与同州绅士及各省督抚治下以下诸执事。再是之绎而汲汲焉。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序
西游诗卷序(壬申)
昔者檀君箕子高句丽迭兴吾邦。享国各千年或七百年。而皆都于平壤之浿水。夫以檀君之事言之。其时与尧舜同。然尧舜大圣也。中国之文明盛于是。礼乐既作。百度毕举。日月星辰得其度。山川疆域得其置。有良臣贤辅如皋夔稷禹者出。为之辅理赞化。勒成典谟。至今人讽诵蹈舞。赫赫见古圣之迹。如在目前。而檀君无作也。无所徵也。是犹中国有巢燧人之世。其民蠢而无知。无大惩劝。简于事而遂阙乎书契耶。箕子东来。始用夏法。革夷俗则其民目觌圣人之容。耳闻九畴之训。心悦乎圣化而拳拳乎礼义之防。至今其泽犹有入人深者。然而尚无典谟之可详焉。是犹尧舜之时。教化既明。而无博闻君子如孔子者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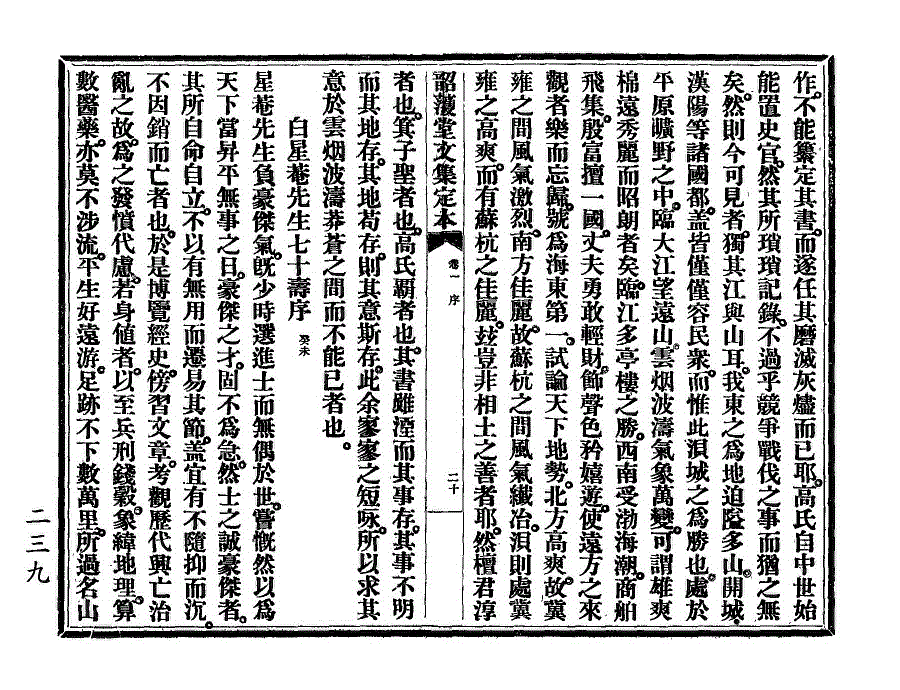 作。不能纂定其书。而遂任其磨灭灰烬而已耶。高氏自中世始能置史官。然其所琐琐记录。不过乎竞争战伐之事而犹之无矣。然则今可见者。独其江与山耳。我东之为地迫隘多山。开城,汉阳等诸国都。盖皆仅仅容民众。而惟此浿城之为胜也。处于平原旷野之中。临大江望远山。云烟波涛气象万变。可谓雄爽棉远秀丽而昭朗者矣。临江多亭楼之胜。西南受渤海潮。商舶飞集。殷富擅一国。丈夫勇敢轻财。饰声色矜嬉游。使远方之来观者乐而忘归。号为海东第一。试论天下地势。北方高爽。故冀雍之间风气激烈。南方佳丽。故苏杭之间风气纤冶。浿则处冀雍之高爽。而有苏杭之佳丽。玆岂非相土之善者耶。然檀君淳者也。箕子圣者也。高氏霸者也。其书虽湮而其事存。其事不明而其地存。其地苟存。则其意斯存。此余寥寥之短咏。所以求其意于云烟波涛莽苍之间而不能已者也。
作。不能纂定其书。而遂任其磨灭灰烬而已耶。高氏自中世始能置史官。然其所琐琐记录。不过乎竞争战伐之事而犹之无矣。然则今可见者。独其江与山耳。我东之为地迫隘多山。开城,汉阳等诸国都。盖皆仅仅容民众。而惟此浿城之为胜也。处于平原旷野之中。临大江望远山。云烟波涛气象万变。可谓雄爽棉远秀丽而昭朗者矣。临江多亭楼之胜。西南受渤海潮。商舶飞集。殷富擅一国。丈夫勇敢轻财。饰声色矜嬉游。使远方之来观者乐而忘归。号为海东第一。试论天下地势。北方高爽。故冀雍之间风气激烈。南方佳丽。故苏杭之间风气纤冶。浿则处冀雍之高爽。而有苏杭之佳丽。玆岂非相土之善者耶。然檀君淳者也。箕子圣者也。高氏霸者也。其书虽湮而其事存。其事不明而其地存。其地苟存。则其意斯存。此余寥寥之短咏。所以求其意于云烟波涛莽苍之间而不能已者也。白星庵先生七十寿序(癸未)
星庵先生负豪杰气。既少时选进士而无偶于世。尝慨然以为天下当升平无事之日。豪杰之才。固不为急。然士之诚豪杰者。其所自命自立。不以有无用而迁易其节。盖宜有不随抑而沉。不因销而亡者也。于是博览经史。傍习文章。考观历代兴亡治乱之故。为之发愤代虑。若身值者。以至兵刑钱谷。象纬地理。算数医药。亦莫不涉流。平生好远游。足迹不下数万里。所过名山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0H 页
 大海关隘之所会。储胥之所当置。往往登高望而继以踌躇。时出以语人。群居稠众之中。议论英发。指画明辨。固已气盖一世。虽流俗或相疑惑呰嗷而不少沮。盖其志之远如此。而年今已七十矣。其初度为二月九日。先生会宾客于杏溪之上。既罢。以其事语泽荣曰。序之去年。国家以外交事兴。大开用人之路。有一达官素重先生而病其老。荐授郎衔以奖之而止。泽荣窃独怪夫天下之物。固有甚相悬。而人思之不深。今夫蒲柳望秋而落。忽焉而朽败。松柏则不然。出于蓬蒿十寻而未已。雨露濡之不加盛。霜雪悴之不加衰。苟无意外之患。愈老而愈壮。一朝去为明堂太庙万乘之所用。今先生之道。将无与此类耶。年七十所。啖食尚能兼数人。目视炯然。百骸九窍畅健而调适。三二十年之人所不如也。不可谓已老矣。天下之事故。烦剧纷纠。凡可以权心程虑者。靡不更阅。一日施诸事业。必将沛然如驾轻车而就熟路。不可谓不可用也。秦之蹇叔。楚之申叔时。当时之人。倚为蓍龟。以决疑贰。汉李固荐樊英。黄琼云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年少。无一宿儒可备顾问。古人之重老成如此。而今遽欲以老废先生。其无乃不量天下豪杰之气。而槩松柏于蒲柳也耶。且使先生自今以往。尚数十年康强无恙。而国家之务不加治。则向之病老者。适其盛壮之时。而事之已谬。亦不可追。吾又未见计之得也。然老聃,庄周。古之达者也。而其书多以远害无
大海关隘之所会。储胥之所当置。往往登高望而继以踌躇。时出以语人。群居稠众之中。议论英发。指画明辨。固已气盖一世。虽流俗或相疑惑呰嗷而不少沮。盖其志之远如此。而年今已七十矣。其初度为二月九日。先生会宾客于杏溪之上。既罢。以其事语泽荣曰。序之去年。国家以外交事兴。大开用人之路。有一达官素重先生而病其老。荐授郎衔以奖之而止。泽荣窃独怪夫天下之物。固有甚相悬。而人思之不深。今夫蒲柳望秋而落。忽焉而朽败。松柏则不然。出于蓬蒿十寻而未已。雨露濡之不加盛。霜雪悴之不加衰。苟无意外之患。愈老而愈壮。一朝去为明堂太庙万乘之所用。今先生之道。将无与此类耶。年七十所。啖食尚能兼数人。目视炯然。百骸九窍畅健而调适。三二十年之人所不如也。不可谓已老矣。天下之事故。烦剧纷纠。凡可以权心程虑者。靡不更阅。一日施诸事业。必将沛然如驾轻车而就熟路。不可谓不可用也。秦之蹇叔。楚之申叔时。当时之人。倚为蓍龟。以决疑贰。汉李固荐樊英。黄琼云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年少。无一宿儒可备顾问。古人之重老成如此。而今遽欲以老废先生。其无乃不量天下豪杰之气。而槩松柏于蒲柳也耶。且使先生自今以往。尚数十年康强无恙。而国家之务不加治。则向之病老者。适其盛壮之时。而事之已谬。亦不可追。吾又未见计之得也。然老聃,庄周。古之达者也。而其书多以远害无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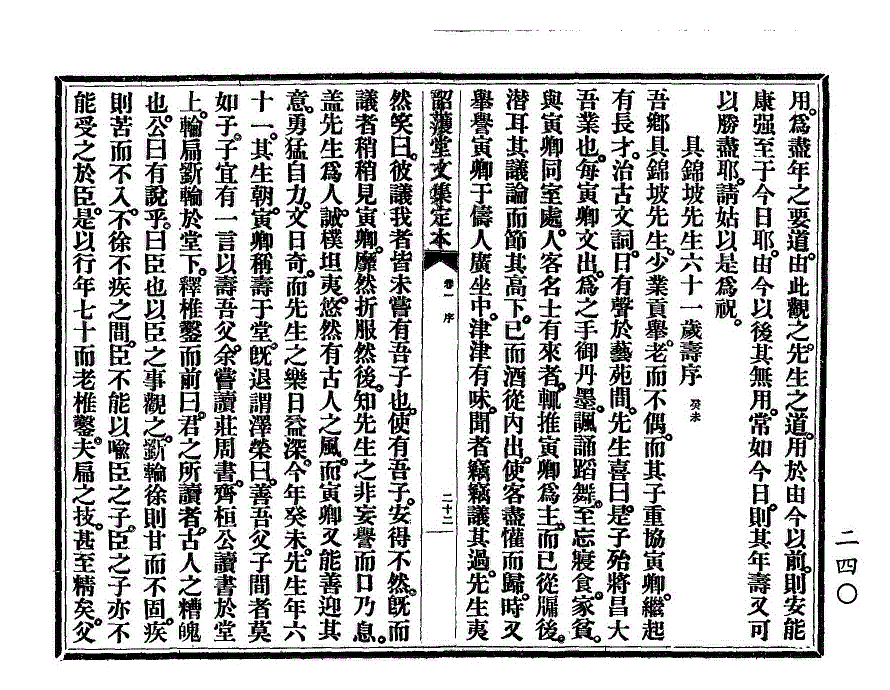 用。为尽年之要道。由此观之。先生之道。用于由今以前。则安能康强至于今日耶。由今以后其无用。常如今日。则其年寿又可以胜尽耶。请姑以是为祝。
用。为尽年之要道。由此观之。先生之道。用于由今以前。则安能康强至于今日耶。由今以后其无用。常如今日。则其年寿又可以胜尽耶。请姑以是为祝。具锦坡先生六十一岁寿序(癸未)
吾乡具锦坡先生。少业贡举。老而不偶。而其子重协寅卿。继起有长才。治古文词。日有声于艺苑间。先生喜曰。是子殆将昌大吾业也。每寅卿文出。为之手御丹墨。讽诵蹈舞。至忘寝食。家贫。与寅卿同室处。人客名士有来者。辄推寅卿为主。而已从牖后。潜耳其议论而节其高下。已而酒从内出。使客尽欢而归。时又举誉寅卿于俦人广坐中。津津有味。闻者窃窃议其过。先生夷然笑曰。彼议我者皆未尝有吾子也。使有吾子。安得不然。既而议者稍稍见寅卿。靡然折服然后。知先生之非妄誉而口乃息。盖先生为人。诚朴坦夷。悠然有古人之风。而寅卿又能善迎其意。勇猛自力。文日奇。而先生之乐日益深。今年癸未。先生年六十一。其生朝。寅卿称寿于堂。既退谓泽荣曰。善吾父子间者莫如子。子宜有一言以寿吾父。余尝读庄周书。齐桓公读书于堂上。论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前曰。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也。公曰有说乎。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之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椎凿。夫扁之技。甚至精矣。父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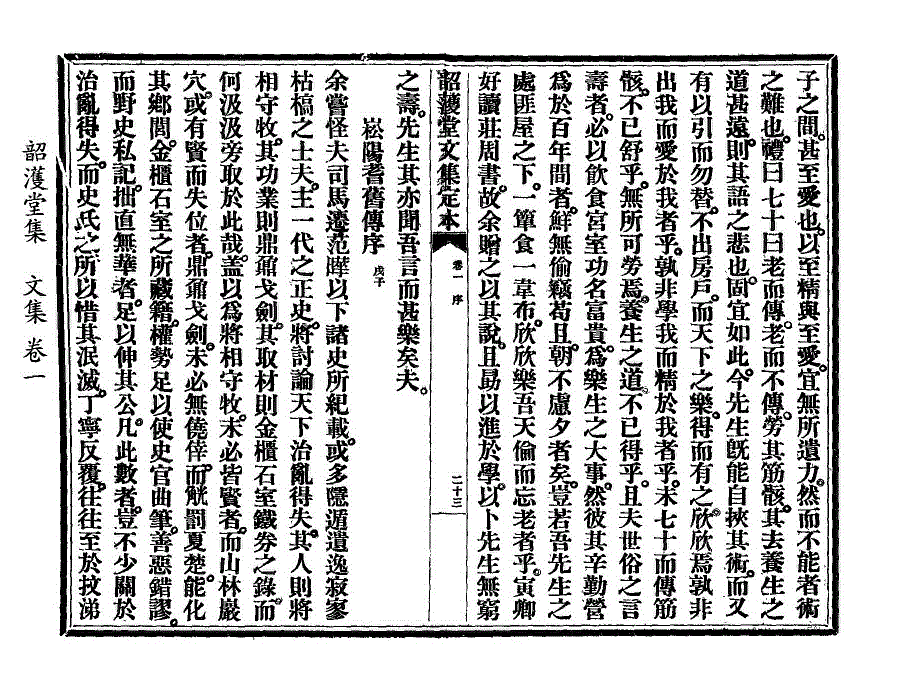 子之间。甚至爱也。以至精与至爱。宜无所遗力。然而不能者术之难也。礼曰七十曰老而传。老而不传。劳其筋骸。其去养生之道甚远。则其语之悲也。固宜如此。今先生既能自挟其术。而又有以引而勿替。不出房户。而天下之乐。得而有之。欣欣焉孰非出我而爱于我者乎。孰非学我而精于我者乎。未七十而传筋骸。不已舒乎。无所可劳焉。养生之道。不已得乎。且夫世俗之言寿者。必以饮食宫室功名富贵。为乐生之大事。然彼其辛勤营为于百年间者。鲜无偷窃苟且。朝不虑夕者矣。岂若吾先生之处匪屋之下。一箪食一韦布。欣欣乐吾天伦而忘老者乎。寅卿好读庄周书。故余赠之以其说。且勖以进于学。以卜先生无穷之寿。先生其亦闻吾言而甚乐矣夫。
子之间。甚至爱也。以至精与至爱。宜无所遗力。然而不能者术之难也。礼曰七十曰老而传。老而不传。劳其筋骸。其去养生之道甚远。则其语之悲也。固宜如此。今先生既能自挟其术。而又有以引而勿替。不出房户。而天下之乐。得而有之。欣欣焉孰非出我而爱于我者乎。孰非学我而精于我者乎。未七十而传筋骸。不已舒乎。无所可劳焉。养生之道。不已得乎。且夫世俗之言寿者。必以饮食宫室功名富贵。为乐生之大事。然彼其辛勤营为于百年间者。鲜无偷窃苟且。朝不虑夕者矣。岂若吾先生之处匪屋之下。一箪食一韦布。欣欣乐吾天伦而忘老者乎。寅卿好读庄周书。故余赠之以其说。且勖以进于学。以卜先生无穷之寿。先生其亦闻吾言而甚乐矣夫。崧阳耆旧传序(戊子)
余尝怪夫司马迁,范晔以下诸史所纪载。或多隐遁遗逸寂寥枯槁之士夫。主一代之正史。将讨论天下治乱得失。其人则将相守牧。其功业则鼎鼐戈剑。其取材则金匮石室铁券之录。而何汲汲旁取于此哉。盖以为将相守牧。未必皆贤者。而山林岩穴。或有贤而失位者。鼎鼐戈剑。未必无侥倖。而觥罚夏楚。能化其乡闾。金匮石室之所藏籍。权势足以使史官曲笔。善恶错谬。而野史私记。拙直无华者。足以伸其公。凡此数者。岂不少关于治乱得失。而史氏之所以惜其泯灭。丁宁反覆。往往至于抆涕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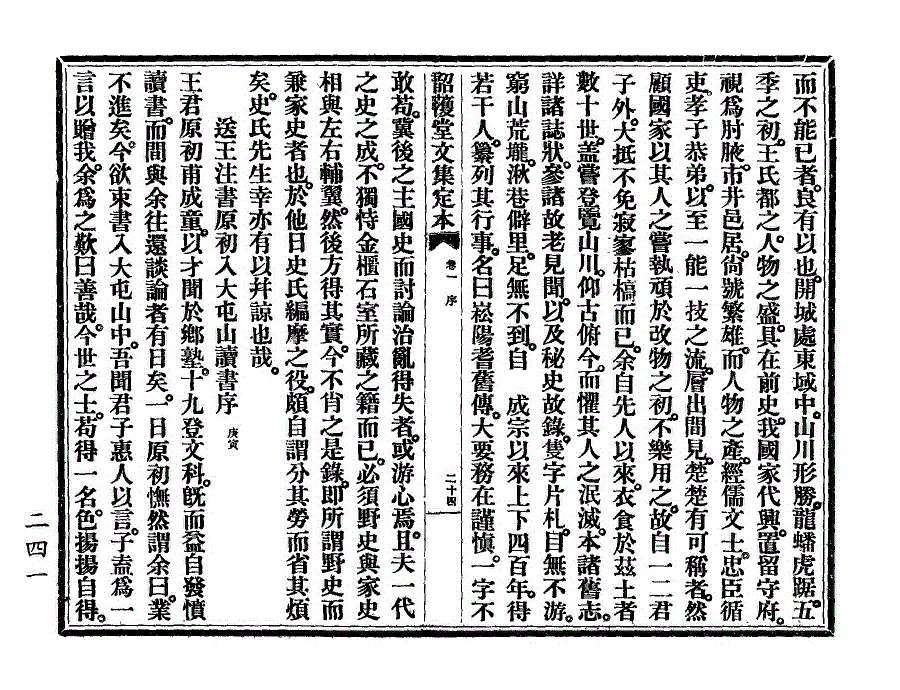 而不能已者。良有以也。开城处东域中。山川形胜。龙蟠虎踞。五季之初。王氏都之。人物之盛。具在前史。我国家代兴。置留守府。视为肘腋。市井邑居。尚号繁雄。而人物之产。经儒文士。忠臣循吏。孝子恭弟。以至一能一技之流。层出间见。楚楚有可称者。然顾国家以其人之尝执顽于改物之初。不乐用之。故自一二君子外。大抵不免寂寥枯槁而已。余自先人以来。衣食于兹土者数十世。盖尝登览山川。仰古俯今。而惧其人之泯灭。本诸旧志。详诸志状。参诸故老见闻。以及秘史故录。只字片札。目无不游。穷山荒垄。湫巷僻里。足无不到。自 成宗以来上下四百年。得若干人。纂列其行事。名曰崧阳耆旧传。大要务在谨慎。一字不敢苟。冀后之主国史而讨论治乱得失者。或游心焉。且夫一代之史之成。不独恃金匮石室所藏之籍而已。必须野史与家史相与左右辅翼。然后方得其实。今不肖之是录。即所谓野史而兼家史者也。于他日史氏编摩之役。颇自谓分其劳而省其烦矣。史氏先生幸亦有以并谅也哉。
而不能已者。良有以也。开城处东域中。山川形胜。龙蟠虎踞。五季之初。王氏都之。人物之盛。具在前史。我国家代兴。置留守府。视为肘腋。市井邑居。尚号繁雄。而人物之产。经儒文士。忠臣循吏。孝子恭弟。以至一能一技之流。层出间见。楚楚有可称者。然顾国家以其人之尝执顽于改物之初。不乐用之。故自一二君子外。大抵不免寂寥枯槁而已。余自先人以来。衣食于兹土者数十世。盖尝登览山川。仰古俯今。而惧其人之泯灭。本诸旧志。详诸志状。参诸故老见闻。以及秘史故录。只字片札。目无不游。穷山荒垄。湫巷僻里。足无不到。自 成宗以来上下四百年。得若干人。纂列其行事。名曰崧阳耆旧传。大要务在谨慎。一字不敢苟。冀后之主国史而讨论治乱得失者。或游心焉。且夫一代之史之成。不独恃金匮石室所藏之籍而已。必须野史与家史相与左右辅翼。然后方得其实。今不肖之是录。即所谓野史而兼家史者也。于他日史氏编摩之役。颇自谓分其劳而省其烦矣。史氏先生幸亦有以并谅也哉。送王注书原初入大屯山读书序(庚寅)
王君原初甫成童。以才闻于乡塾。十九登文科。既而益自发愤读书。而间与余往还谈论者有日矣。一日原初怃然谓余曰。业不进矣。今欲束书入大屯山中。吾闻君子惠人以言。子盍为一言以赠我。余为之叹曰善哉。今世之士。苟得一名。色扬扬自得。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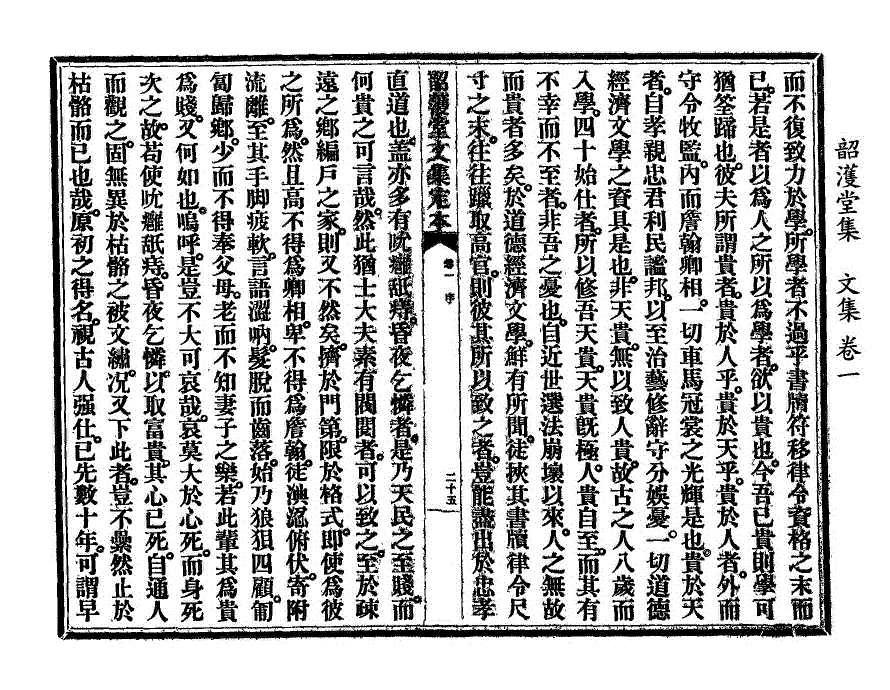 而不复致力于学。所学者不过乎书牍符移律令资格之末而已。若是者以为人之所以为学者。欲以贵也。今吾已贵则学可犹筌蹄也。彼夫所谓贵者。贵于人乎。贵于天乎。贵于人者。外而守令牧监。内而詹翰卿相。一切车马冠裳之光辉是也。贵于天者。自孝亲忠君利民谧邦。以至治艺修辞守分娱忧。一切道德经济文学之资具是也。非天贵。无以致人贵。故古之人八岁而入学。四十始仕者。所以修吾天贵。天贵既极。人贵自至。而其有不幸而不至者。非吾之忧也。自近世选法崩坏以来。人之无故而贵者多矣。于道德经济文学。鲜有所闻。徒挟其书牍律令尺寸之末。往往躐取高官。则彼其所以致之者。岂能尽出于忠孝直道也。盖亦多有吮痈舐痔。昏夜乞怜者。是乃天民之至贱。而何贵之可言哉。然此犹士大夫素有阀阅者。可以致之。至于疏远之乡编户之家。则又不然矣。挤于门第。限于格式。即使为彼之所为。然且高不得为卿相。卑不得为詹翰。徒淟涊俯伏。寄附流离。至其手脚疲软。言语涩呐。发脱而齿落。始乃狼狈四顾。匍匐归乡。少而不得奉父母。老而不知妻子之乐。若此辈其为贵为贱。又何如也。呜呼。是岂不大可哀哉。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故苟使吮痈舐痔。昏夜乞怜。以取富贵。其心已死。自通人而观之。固无异于枯骼之被文绣。况又下此者。岂不累然止于枯骼而已也哉。原初之得名。视古人强仕。已先数十年。可谓早
而不复致力于学。所学者不过乎书牍符移律令资格之末而已。若是者以为人之所以为学者。欲以贵也。今吾已贵则学可犹筌蹄也。彼夫所谓贵者。贵于人乎。贵于天乎。贵于人者。外而守令牧监。内而詹翰卿相。一切车马冠裳之光辉是也。贵于天者。自孝亲忠君利民谧邦。以至治艺修辞守分娱忧。一切道德经济文学之资具是也。非天贵。无以致人贵。故古之人八岁而入学。四十始仕者。所以修吾天贵。天贵既极。人贵自至。而其有不幸而不至者。非吾之忧也。自近世选法崩坏以来。人之无故而贵者多矣。于道德经济文学。鲜有所闻。徒挟其书牍律令尺寸之末。往往躐取高官。则彼其所以致之者。岂能尽出于忠孝直道也。盖亦多有吮痈舐痔。昏夜乞怜者。是乃天民之至贱。而何贵之可言哉。然此犹士大夫素有阀阅者。可以致之。至于疏远之乡编户之家。则又不然矣。挤于门第。限于格式。即使为彼之所为。然且高不得为卿相。卑不得为詹翰。徒淟涊俯伏。寄附流离。至其手脚疲软。言语涩呐。发脱而齿落。始乃狼狈四顾。匍匐归乡。少而不得奉父母。老而不知妻子之乐。若此辈其为贵为贱。又何如也。呜呼。是岂不大可哀哉。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故苟使吮痈舐痔。昏夜乞怜。以取富贵。其心已死。自通人而观之。固无异于枯骼之被文绣。况又下此者。岂不累然止于枯骼而已也哉。原初之得名。视古人强仕。已先数十年。可谓早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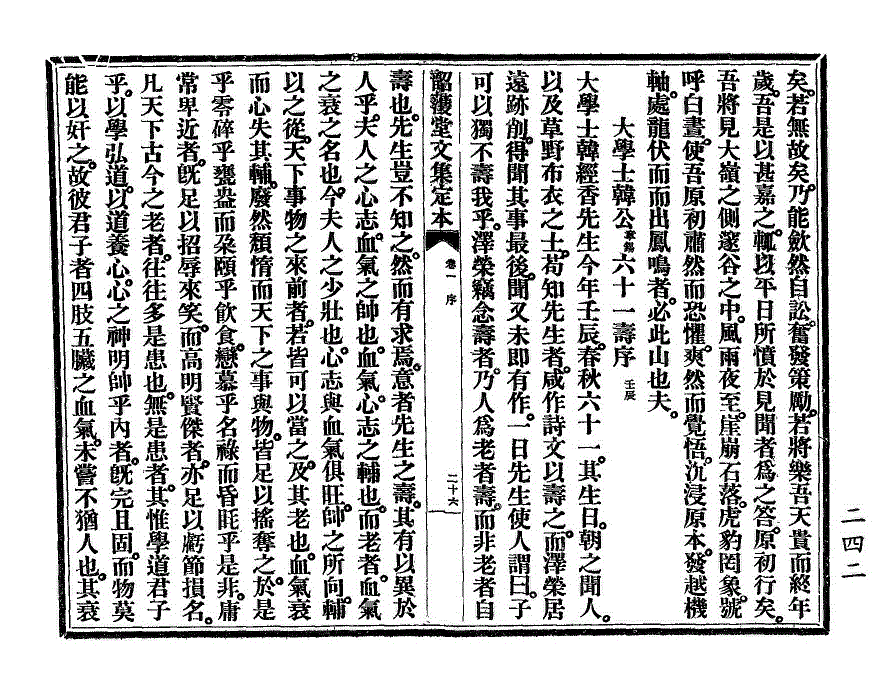 矣。若无故矣。乃能敛然自讼。奋发策励。若将乐吾天贵而终年岁。吾是以甚嘉之。辄以平日所愤于见闻者为之答。原初行矣。吾将见大岭之侧邃谷之中。风雨夜至。崖崩石落。虎豹罔象。号呼白昼。使吾原初肃然而恐惧。爽然而觉悟。沉浸原本。发越机轴。处龙伏而而出凤鸣者。必此山也夫。
矣。若无故矣。乃能敛然自讼。奋发策励。若将乐吾天贵而终年岁。吾是以甚嘉之。辄以平日所愤于见闻者为之答。原初行矣。吾将见大岭之侧邃谷之中。风雨夜至。崖崩石落。虎豹罔象。号呼白昼。使吾原初肃然而恐惧。爽然而觉悟。沉浸原本。发越机轴。处龙伏而而出凤鸣者。必此山也夫。大学士韩公(章锡)六十一寿序(壬辰)
大学士韩经香先生今年壬辰。春秋六十一。其生日。朝之闻人。以及草野布衣之士。苟知先生者。咸作诗文以寿之。而泽荣居远迹削。得闻其事最后。闻又未即有作。一日先生使人谓曰。子可以独不寿我乎。泽荣窃念寿者。乃人为老者寿。而非老者自寿也。先生岂不知之。然而有求焉。意者先生之寿。其有以异于人乎。夫人之心志。血气之帅也。血气。心志之辅也。而老者。血气之衰之名也。今夫人之少壮也。心志与血气俱旺。帅之所向。辅以之从。天下事物之来前者。若皆可以当之。及其老也。血气衰而心失其辅。废然颓惰而天下之事与物。皆足以摇夺之。于是乎零碎乎瓮盎而朵颐乎饮食。恋慕乎名禄而昏眊乎是非。庸常卑近者。既足以招辱来笑。而高明贤杰者。亦足以亏节损名。凡天下古今之老者。往往多是患也。无是患者。其惟学道君子乎。以学弘道。以道养心。心之神明帅乎内者。既完且固。而物莫能以奸之。故彼君子者四肢五脏之血气。未尝不犹人也。其衰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一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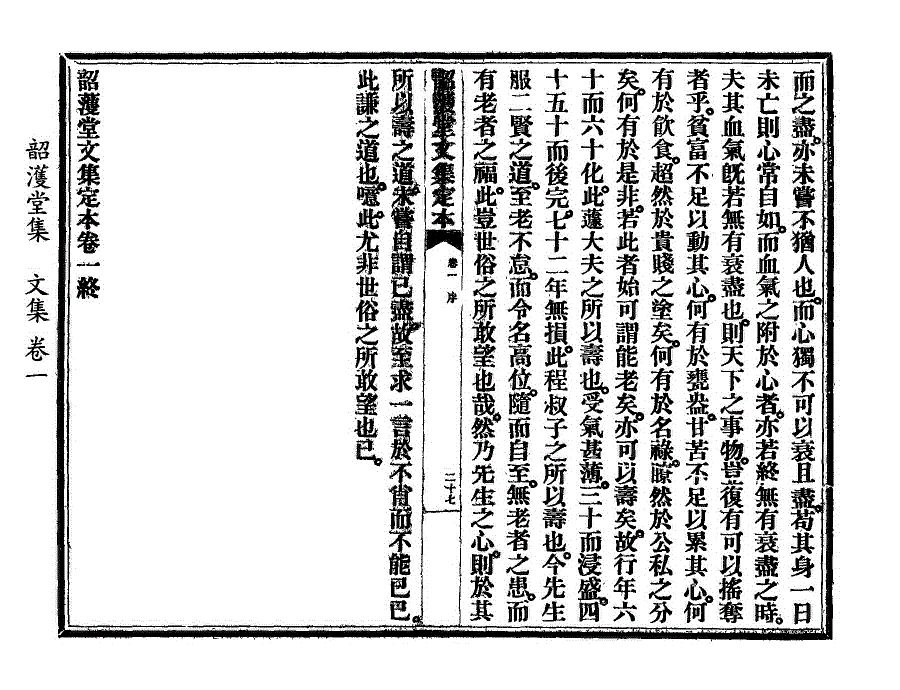 而之尽。亦未尝不犹人也。而心独不可以衰且尽。苟其身一日未亡则心常自如。而血气之附于心者。亦若终无有衰尽之时。夫其血气既若无有衰尽也。则天下之事物。岂复有可以摇夺者乎。贫富不足以动其心。何有于瓮盎。甘苦不足以累其心。何有于饮食。超然于贵贱之涂矣。何有于名禄。瞭然于公私之分矣。何有于是非。若此者始可谓能老矣。亦可以寿矣。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蘧大夫之所以寿也。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七十二年无损。此程叔子之所以寿也。今先生服二贤之道。至老不怠。而令名高位。随而自至。无老者之患。而有老者之福。此岂世俗之所敢望也哉。然乃先生之心。则于其所以寿之道。未尝自谓已尽。故至求一言于不肖而不能已已。此谦之道也。噫。此尤非世俗之所敢望也已。
而之尽。亦未尝不犹人也。而心独不可以衰且尽。苟其身一日未亡则心常自如。而血气之附于心者。亦若终无有衰尽之时。夫其血气既若无有衰尽也。则天下之事物。岂复有可以摇夺者乎。贫富不足以动其心。何有于瓮盎。甘苦不足以累其心。何有于饮食。超然于贵贱之涂矣。何有于名禄。瞭然于公私之分矣。何有于是非。若此者始可谓能老矣。亦可以寿矣。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蘧大夫之所以寿也。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七十二年无损。此程叔子之所以寿也。今先生服二贤之道。至老不怠。而令名高位。随而自至。无老者之患。而有老者之福。此岂世俗之所敢望也哉。然乃先生之心。则于其所以寿之道。未尝自谓已尽。故至求一言于不肖而不能已已。此谦之道也。噫。此尤非世俗之所敢望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