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中庸讲议条对[一]( 奎章阁讲制时)
中庸讲议条对[一]( 奎章阁讲制时)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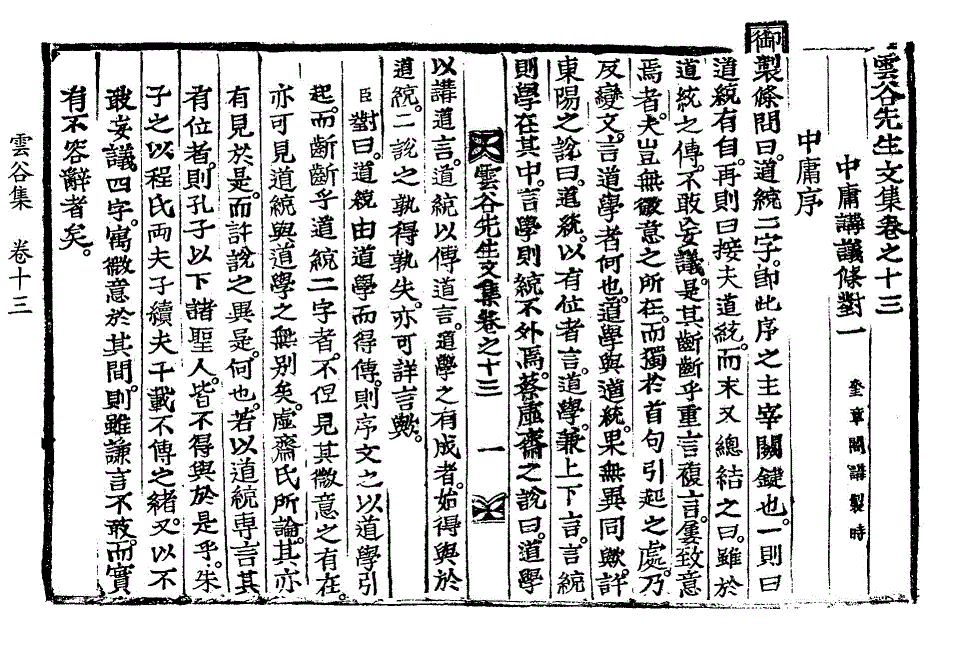 中庸序
中庸序御制条问曰。道统二字。即此序之主宰关键也。一则曰道统有自。再则曰接夫道统。而末又总结之曰。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是其龂龂乎重言复言。屡致意焉者。夫岂无微意之所在。而独于首句引起之处。乃反变文。言道学者何也。道学与道统。果无异同欤。许东阳之说曰。道统。以有位者言。道学。兼上下言。言统则学在其中。言学则统不外焉。蔡虚斋之说曰。道学以讲道言。道统以传道言。道学之有成者。始得与于道统。二说之孰得孰失。亦可详言欤。
臣对曰。道统由道学而得传。则序文之以道学引起。而龂龂乎道统二字者。不但见其微意之有在。亦可见道统与道学之无别矣。虚斋氏所论。其亦有见于是。而许说之异是。何也。若以道统专言其有位者。则孔子以下诸圣人。皆不得与于是乎。朱子之以程氏两夫子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又以不敢妄议四字。寓微意于其间。则虽谦言不敢。而实有不容辞者矣。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3L 页
 御制条问曰。人心道心之为儒家说丛也久矣。盖自朱子主气主理之说引而不发之后。当时及门之士。已有歧异之论。黄勉斋尝以喜怒哀乐为人心。仁义礼智为道心。与李公晦贻书辨论。而其所谓喜怒哀乐之不可为道心者。较诸朱子所谓当喜怒而喜怒者为道心之训。则已相去径庭矣。夫以勉斋之嫡传。而犹如此。则况于其他乎。逮夫东儒。其说益繁。人心。气发而理乘。道心。理发而气随者。退陶李滉之说也。人心道心。同是气发理乘。而发者即气。所以发者即理者。栗谷李珥之说也。而或有并诋二说者曰。退陶知人心道心有主气主理之分。而独不知理与气之浑融无间。元不相离。故理发气随之说。失之名言之间。栗谷知人心道心之同是气发理乘。而独不知发之之时。已有理乘气。气寓理之不同。故于为人为道之间。未能分明劈破。是数说者。胥相甲乙。聚讼不已。而至于今。四七人道之辨。浩如烟海。莫可穷诘。果可以反覆讨论而历辨详覈耶。
御制条问曰。人心道心之为儒家说丛也久矣。盖自朱子主气主理之说引而不发之后。当时及门之士。已有歧异之论。黄勉斋尝以喜怒哀乐为人心。仁义礼智为道心。与李公晦贻书辨论。而其所谓喜怒哀乐之不可为道心者。较诸朱子所谓当喜怒而喜怒者为道心之训。则已相去径庭矣。夫以勉斋之嫡传。而犹如此。则况于其他乎。逮夫东儒。其说益繁。人心。气发而理乘。道心。理发而气随者。退陶李滉之说也。人心道心。同是气发理乘。而发者即气。所以发者即理者。栗谷李珥之说也。而或有并诋二说者曰。退陶知人心道心有主气主理之分。而独不知理与气之浑融无间。元不相离。故理发气随之说。失之名言之间。栗谷知人心道心之同是气发理乘。而独不知发之之时。已有理乘气。气寓理之不同。故于为人为道之间。未能分明劈破。是数说者。胥相甲乙。聚讼不已。而至于今。四七人道之辨。浩如烟海。莫可穷诘。果可以反覆讨论而历辨详覈耶。臣对曰。人心道心之说。发于舜禹。而四端七情之训。发于思孟。此固圣学之源头。义理之根柢。而主理主气之说。便作吾儒家一副当大议论。如黄勉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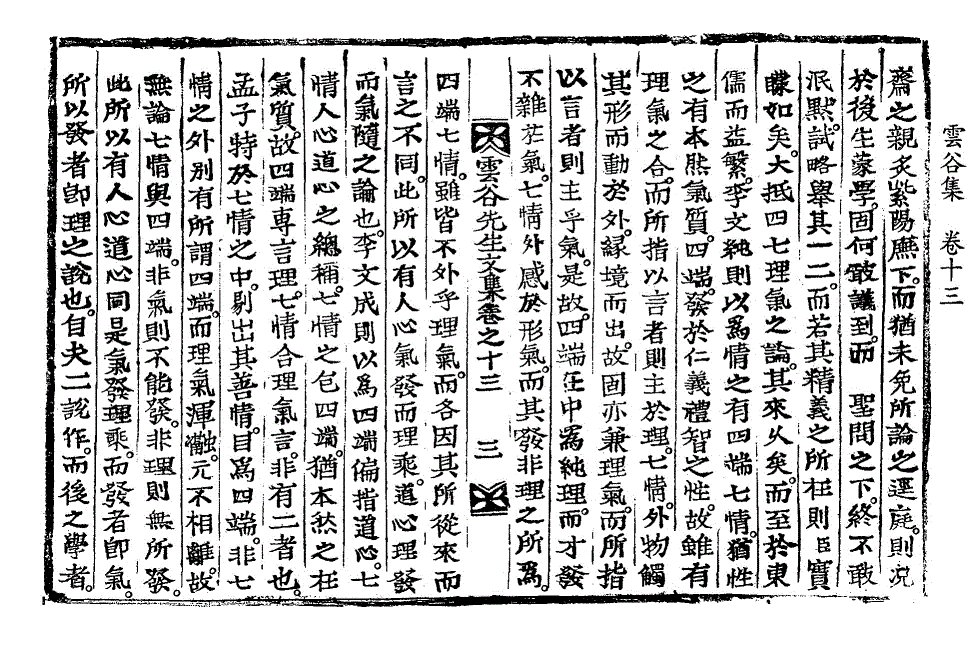 斋之亲炙紫阳庑下。而犹未免所论之径庭。则况于后生蒙学。固何敢议到。而 圣问之下。终不敢泯默。试略举其一二。而若其精义之所在则臣实矇如矣。大抵四七理气之论。其来久矣。而至于东儒而益繁。李文纯则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犹性之有本然气质。四端。发于仁义礼智之性。故虽有理气之合。而所指以言者则主于理。七情。外物触其形而动于外。缘境而出。故固亦兼理气。而所指以言者则主乎气。是故。四端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不杂于气。七情外感于形气。而其发非理之所为。四端七情。虽皆不外乎理气。而各因其所从来而言之不同。此所以有人心气发而理乘。道心理发而气随之论也。李文成则以为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总称。七情之包四端。犹本然之在气质。故四端专言理。七情合理气言。非有二者也。孟子特于七情之中。剔出其善情。目为四端。非七情之外别有所谓四端。而理气浑融。元不相离。故无论七情与四端。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此所以有人心道心同是气发理乘。而发者即气。所以发者即理之说也。自夫二说作。而后之学者。
斋之亲炙紫阳庑下。而犹未免所论之径庭。则况于后生蒙学。固何敢议到。而 圣问之下。终不敢泯默。试略举其一二。而若其精义之所在则臣实矇如矣。大抵四七理气之论。其来久矣。而至于东儒而益繁。李文纯则以为情之有四端七情。犹性之有本然气质。四端。发于仁义礼智之性。故虽有理气之合。而所指以言者则主于理。七情。外物触其形而动于外。缘境而出。故固亦兼理气。而所指以言者则主乎气。是故。四端在中为纯理。而才发不杂于气。七情外感于形气。而其发非理之所为。四端七情。虽皆不外乎理气。而各因其所从来而言之不同。此所以有人心气发而理乘。道心理发而气随之论也。李文成则以为四端偏指道心。七情人心道心之总称。七情之包四端。犹本然之在气质。故四端专言理。七情合理气言。非有二者也。孟子特于七情之中。剔出其善情。目为四端。非七情之外别有所谓四端。而理气浑融。元不相离。故无论七情与四端。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此所以有人心道心同是气发理乘。而发者即气。所以发者即理之说也。自夫二说作。而后之学者。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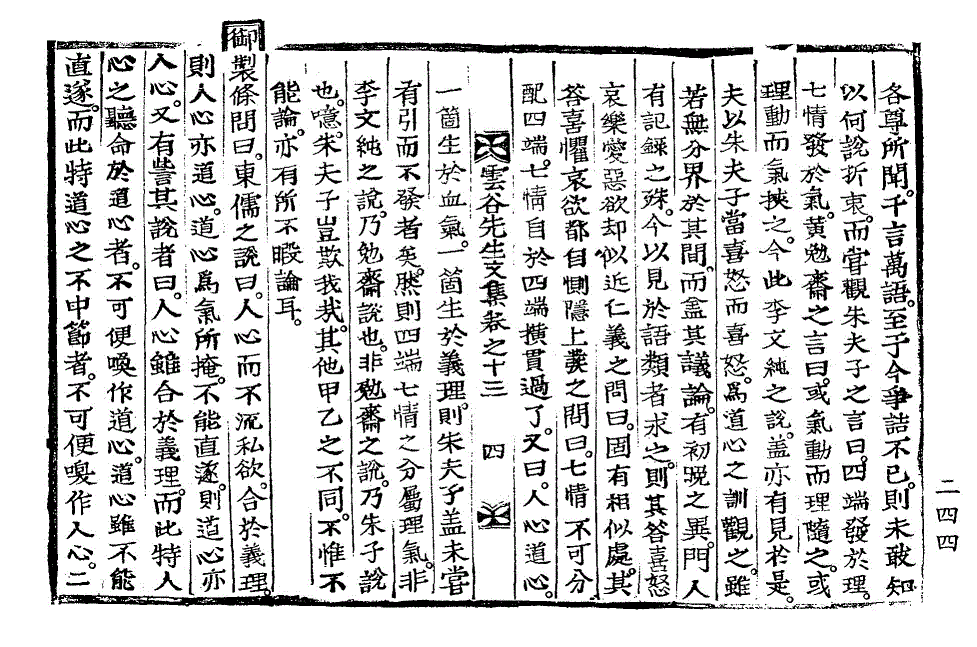 各尊所闻。千言万语。至于今争诘不已。则未敢知以何说折衷。而尝观朱夫子之言曰。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黄勉斋之言曰。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今此李文纯之说。盖亦有见于是。夫以朱夫子当喜怒而喜怒。为道心之训观之。虽若无分界于其间。而盖其议论。有初晚之异。门人有记录之殊。今以见于语类者求之。则其答喜怒哀乐爱恶欲却似近仁义之问曰。固有相似处。其答喜惧哀欲都自恻隐上发之问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又曰。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则朱夫子盖未尝有引而不发者矣。然则四端七情之分属理气。非李文纯之说。乃勉斋说也。非勉斋之说。乃朱子说也。噫。朱夫子岂欺我哉。其他甲乙之不同。不惟不能论。亦有所不暇论耳。
各尊所闻。千言万语。至于今争诘不已。则未敢知以何说折衷。而尝观朱夫子之言曰。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黄勉斋之言曰。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今此李文纯之说。盖亦有见于是。夫以朱夫子当喜怒而喜怒。为道心之训观之。虽若无分界于其间。而盖其议论。有初晚之异。门人有记录之殊。今以见于语类者求之。则其答喜怒哀乐爱恶欲却似近仁义之问曰。固有相似处。其答喜惧哀欲都自恻隐上发之问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又曰。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则朱夫子盖未尝有引而不发者矣。然则四端七情之分属理气。非李文纯之说。乃勉斋说也。非勉斋之说。乃朱子说也。噫。朱夫子岂欺我哉。其他甲乙之不同。不惟不能论。亦有所不暇论耳。御制条问曰。东儒之说曰。人心而不流私欲。合于义理。则人心亦道心。道心为气所掩。不能直遂。则道心亦人心。又有訾其说者曰。人心虽合于义理。而此特人心之听命于道心者。不可便唤作道心。道心虽不能直遂。而此特道心之不中节者。不可便唤作人心。二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5H 页
 说之中。何者为得欤。由前之说。有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而一念之间。公私错杂。得不几于囫囵纷纠之病。由后之说则人心道心截有界限。而性有二发。情有二本。亦无近于支离分裂之讥欤。不然而外是二说。拈出真解。则将如何立说而可。
说之中。何者为得欤。由前之说。有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而一念之间。公私错杂。得不几于囫囵纷纠之病。由后之说则人心道心截有界限。而性有二发。情有二本。亦无近于支离分裂之讥欤。不然而外是二说。拈出真解。则将如何立说而可。臣对曰。人心生于形气。道心原于性命。则固可以分言。道心主于人心。人心听于道心。则亦可以合言。今若谓人心而合于义理。则人心亦道心。道心不能直遂。则道心亦人心云尔。则是上智无人心。下愚无道心。而或源或生之异其名者。混而无别。又若谓人心虽合于义理。而此特人心之听命。不可便唤作道心。道心虽不能直遂。而此特道心之不中节。不可便唤作人心。则是道心无与于饮食衣服。人心不资于本源性命。而相资相发之不相离者。判而为二。其必曰喜怒哀乐是人心。而喜怒哀乐之得其正。则人心亦资道心。恻隐羞恶是道心。而恻隐羞恶之所附丽。则道心亦资人心。然后方可谓合言而不为一。分言而不为二。而庶乎免囫囵分裂之讥。李文纯尝谓人心道心固可分言而亦不可判然作二物。斯可谓拈出真解矣。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5L 页
 御制条问曰。危者。安之反。微者。著之反。人心惟危则道心之安可知矣。道心惟微则人心之著可知矣。然则圣人之不以安对危。以著对微。而却以危与微对说者。岂亦互文以见意耶。抑别有义意在欤。程子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道心之为天理。固无间然。而人心之为人欲。则尚有可疑者。盖饥而思食。渴而思饮。掐则觉痛。抓则觉痒。即圣凡之所同。而朱子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也。岂可以人心直归之人欲哉。且周濂溪尝以孟子寡欲之训。谓犹有未尽曰。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今若谓人心即是人欲则是将绝去之不暇。又岂但曰危而已乎。是以。语类有曰人心本无不善。又曰。危未便是不好。此可见朱子之微意。而及其为延和殿奏劄。则又却以人心为人欲者。何也。同出于朱子。而有此参商。将谁使之折衷哉。
御制条问曰。危者。安之反。微者。著之反。人心惟危则道心之安可知矣。道心惟微则人心之著可知矣。然则圣人之不以安对危。以著对微。而却以危与微对说者。岂亦互文以见意耶。抑别有义意在欤。程子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道心之为天理。固无间然。而人心之为人欲。则尚有可疑者。盖饥而思食。渴而思饮。掐则觉痛。抓则觉痒。即圣凡之所同。而朱子所谓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者也。岂可以人心直归之人欲哉。且周濂溪尝以孟子寡欲之训。谓犹有未尽曰。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今若谓人心即是人欲则是将绝去之不暇。又岂但曰危而已乎。是以。语类有曰人心本无不善。又曰。危未便是不好。此可见朱子之微意。而及其为延和殿奏劄。则又却以人心为人欲者。何也。同出于朱子。而有此参商。将谁使之折衷哉。臣对曰。安与危。当于人心上对。微与著。当于道心上对。人心欲其安。故言其危。道心欲其著。故言其微。真西山曰。人心之发。如铦锋如悍马。有未易制驭者。故危。道心之发。如火始然。如泉始达。有未易充广者。故微。各就其偏重处言。而有此危与微之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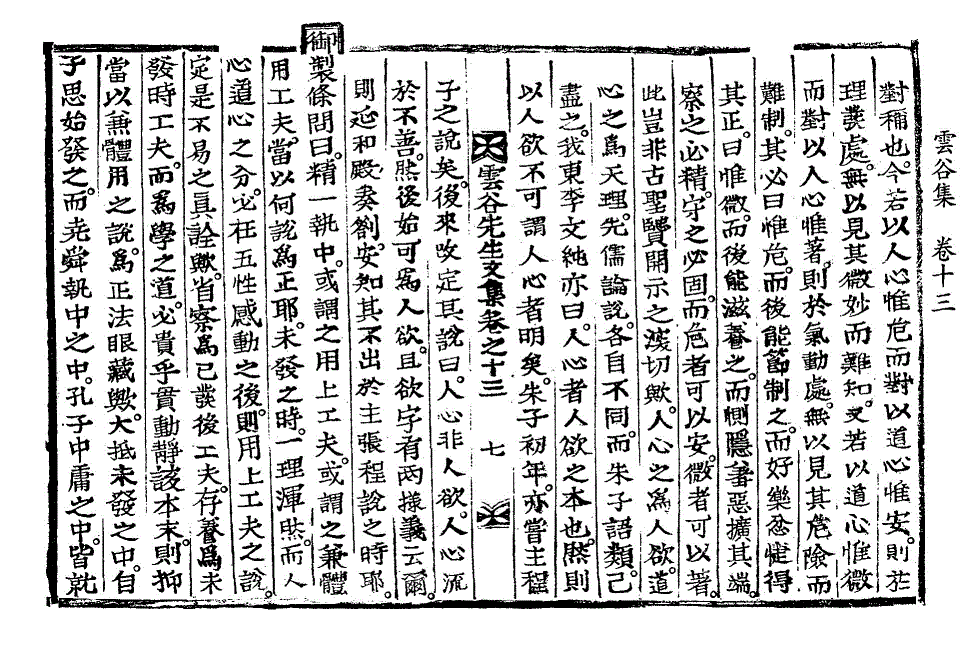 对称也。今若以人心惟危而对以道心惟安。则于理发处。无以见其微妙而难知。又若以道心惟微而对以人心惟著。则于气动处。无以见其危险而难制。其必曰惟危。而后能节制之。而好乐忿𢜀得其正。曰惟微。而后能滋养之。而恻隐羞恶扩其端。察之必精。守之必固。而危者可以安。微者可以著。此岂非古圣贤开示之深切欤。人心之为人欲。道心之为天理。先儒论说。各自不同。而朱子语类。已尽之。我东李文纯亦曰。人心者人欲之本也。然则以人欲不可谓人心者明矣。朱子初年。亦尝主程子之说矣。后来改定其说曰。人心非人欲。人心流于不善。然后始可为人欲。且欲字有两㨾义云尔。则延和殿奏劄。安知其不出于主张程说之时耶。
对称也。今若以人心惟危而对以道心惟安。则于理发处。无以见其微妙而难知。又若以道心惟微而对以人心惟著。则于气动处。无以见其危险而难制。其必曰惟危。而后能节制之。而好乐忿𢜀得其正。曰惟微。而后能滋养之。而恻隐羞恶扩其端。察之必精。守之必固。而危者可以安。微者可以著。此岂非古圣贤开示之深切欤。人心之为人欲。道心之为天理。先儒论说。各自不同。而朱子语类。已尽之。我东李文纯亦曰。人心者人欲之本也。然则以人欲不可谓人心者明矣。朱子初年。亦尝主程子之说矣。后来改定其说曰。人心非人欲。人心流于不善。然后始可为人欲。且欲字有两㨾义云尔。则延和殿奏劄。安知其不出于主张程说之时耶。御制条问曰。精一执中。或谓之用上工夫。或谓之兼体用工夫。当以何说为正耶。未发之时。一理浑然。而人心道心之分。必在五性感动之后。则用上工夫之说。定是不易之真诠欤。省察为已发后工夫。存养为未发时工夫。而为学之道。必贵乎贯动静该本末。则抑当以兼体用之说。为正法眼藏欤。大抵未发之中。自子思始发之。而尧舜执中之中。孔子中庸之中。皆就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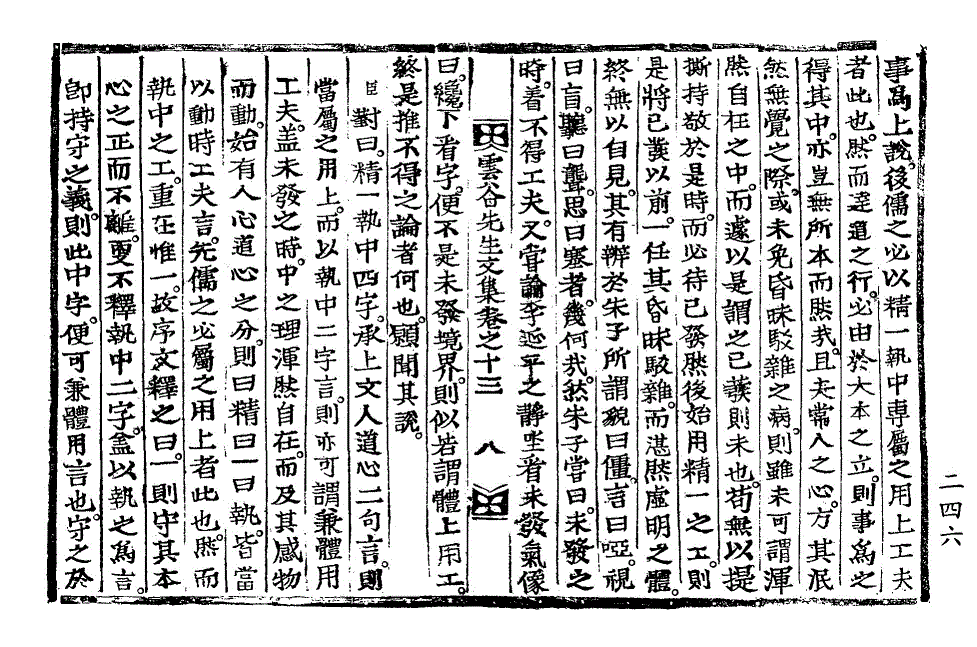 事为上说。后儒之必以精一执中专属之用上工夫者此也。然而达道之行。必由于大本之立。则事为之得其中。亦岂无所本而然哉。且夫常人之心。方其泯然无觉之际。或未免昏昧驳杂之病。则虽未可谓浑然自在之中。而遽以是谓之已发则未也。苟无以提撕持敬于是时。而必待已发然后始用精一之工。则是将已发以前。一任其昏昧驳杂。而湛然虚明之体。终无以自见。其有辨于朱子所谓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者。几何哉。然朱子尝曰。未发之时。着不得工夫。又尝论李延平之静坐看未发气像曰。才下看字。便不是未发境界。则似若谓体上用工。终是推不得之论者何也。愿闻其说。
事为上说。后儒之必以精一执中专属之用上工夫者此也。然而达道之行。必由于大本之立。则事为之得其中。亦岂无所本而然哉。且夫常人之心。方其泯然无觉之际。或未免昏昧驳杂之病。则虽未可谓浑然自在之中。而遽以是谓之已发则未也。苟无以提撕持敬于是时。而必待已发然后始用精一之工。则是将已发以前。一任其昏昧驳杂。而湛然虚明之体。终无以自见。其有辨于朱子所谓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者。几何哉。然朱子尝曰。未发之时。着不得工夫。又尝论李延平之静坐看未发气像曰。才下看字。便不是未发境界。则似若谓体上用工。终是推不得之论者何也。愿闻其说。臣对曰。精一执中四字。承上文人道心二句言。则当属之用上。而以执中二字言。则亦可谓兼体用工夫。盖未发之时。中之理浑然自在。而及其感物而动。始有人心道心之分。则曰精曰一曰执。皆当以动时工夫言。先儒之必属之用上者此也。然而执中之工。重在惟一。故序文释之曰。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更不释执中二字。盖以执之为言。即持守之义。则此中字。便可兼体用言也。守之于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7H 页
 未发之中而大本以立。守之于已发之中而达道以行。在心而为不偏不倚之中。在事而为无过不及之中。则是所谓贯动静该本末。而体用之工。尽在于是矣。然则惟精是省察之意。惟一是存养之意。而此一字。与程子所谓主一。大义无别。盖主一之一。专就未发时存养。此所谓一。即于已发之后。择之既精。守之愈固。而本心之正。常为一身之主。则大本之中已立。而措诸事为。无不得其中矣。此西山所谓知及仁守。相为始终。而精一执中。实为尧舜禹体用之相传也。岂可以人心道心之为已发。而以此四个字。专属之用耶。大抵执中之中。中庸之中。虽就事为上说。而皆本于未发之中。故朱子尝以中庸之中。为兼体用而言。则此中字之亦为兼体用无疑。且夫常人之心。虽与圣人浑然之中有异。而亦岂无未发时节乎。苟于介然无觉之顷。不加澄治之工。而必待已发之后。始用精一之工。则是所谓不浚其源而欲清其流。不培其根而欲达其枝。尚何望其时措之中耶。盖以后之学者看得未发太重。如吕子约有求中之问。司马公有念中之语。故发此以警之。而其于涵养持敬之工。
未发之中而大本以立。守之于已发之中而达道以行。在心而为不偏不倚之中。在事而为无过不及之中。则是所谓贯动静该本末。而体用之工。尽在于是矣。然则惟精是省察之意。惟一是存养之意。而此一字。与程子所谓主一。大义无别。盖主一之一。专就未发时存养。此所谓一。即于已发之后。择之既精。守之愈固。而本心之正。常为一身之主。则大本之中已立。而措诸事为。无不得其中矣。此西山所谓知及仁守。相为始终。而精一执中。实为尧舜禹体用之相传也。岂可以人心道心之为已发。而以此四个字。专属之用耶。大抵执中之中。中庸之中。虽就事为上说。而皆本于未发之中。故朱子尝以中庸之中。为兼体用而言。则此中字之亦为兼体用无疑。且夫常人之心。虽与圣人浑然之中有异。而亦岂无未发时节乎。苟于介然无觉之顷。不加澄治之工。而必待已发之后。始用精一之工。则是所谓不浚其源而欲清其流。不培其根而欲达其枝。尚何望其时措之中耶。盖以后之学者看得未发太重。如吕子约有求中之问。司马公有念中之语。故发此以警之。而其于涵养持敬之工。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7L 页
 盖尝屡言之矣。岂可谓体上用工。终是推不得之论耶。
盖尝屡言之矣。岂可谓体上用工。终是推不得之论耶。御制条问曰。此云必使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其义可详言欤。夫心一而已。而持其所感而发者。有义理形色之不同。故纯于义理者。谓之道心。出于形色者。谓之人心。其实非有二心也。今曰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则是将有一心为之主。又有一心为之听命。而位置较异。界分截然耶。且释氏之观心。吾儒讥之者。以其有以心观心之病也。以心听心。果何异于以心观心。而朱子之言如是。何也。
臣对曰。心一也。而有人道之二名。盖理与气合而为心。故发于理者。谓之道心。发于气者。谓之人心。其实只是一物耳。然其或危或微而不相敌。则于是乎就其已发处。以道心为之主宰。而使人心之横逸者。一听于理。如饥之欲食是人心也。而旋以为不义而不食。则即是听命于道心也。如云克己遏欲。义战之胜。百体之从云尔。非别有两㨾心。一为主一听命。而位置界分之截然较异也。释氏之观心。是就寂然不动处。欲以一心观一心。则所以有二心之讥。而此所谓听命于道心者。是就其已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8H 页
 发处主宰运用之谓。则其言虽若相近。而其旨不啻相反。儒释邪正之分。正于此等处看。
发处主宰运用之谓。则其言虽若相近。而其旨不啻相反。儒释邪正之分。正于此等处看。御制条问曰。此云天命率性。道心之谓也。性与心果若是无别。则王阳明心即理。心即道之说。又何为而群起共诋之也。大抵江西一派之沉溺于顿悟之说。卒未免葱岭气味者。政坐乎认心为性。而罗整庵诸儒之鳃鳃大呼。斥彼之误者。亦惟曰心性无别而已。如使彼之桀黠者。借是说为依据曰。心即理。心即道。朱子之所已言云尔。则将何以置对。是必有似同而实异者。盍各言其素讲者。
臣对曰。理与气合而为心。则就理气浑合之中。而剔出理一边。曰道心。诚是也。若谓之心即理心即道。则是不知理气之合。人道之分也。其可谓成说乎。此云天命率性道心之谓者。即是就此心之中剔出理一边。以證天命率性之纯是道心。其与王阳明之都不知理气合人道分。而语心性无别者。不啻相悬。则以罗整庵之考理未精。犹能斥彼之误矣。若是乎江西一派学之带了葱岭气味也。大抵心一也。而曰道心曰人心。则发于理发于气之自有分界。其不可混而一之也明矣。彼如曰。朱子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8L 页
 之所已言云尔。则为朱子辨之者。将曰。如何而曰道心。如何而曰人心。既有人道之异。则直以心谓理谓道可乎。庶可以證诸彼之桀黠者矣。
之所已言云尔。则为朱子辨之者。将曰。如何而曰道心。如何而曰人心。既有人道之异。则直以心谓理谓道可乎。庶可以證诸彼之桀黠者矣。御制条问曰。孟子之受业子思。其说不一。史记谓受业于子思门人。孔丛子谓亲受业于子思。而赵岐,王劭则主孔丛子之说。司马贞,孔颖达则主史记之说。今考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哀王七年。燕人叛齐。而孟子以是时在齐。距孔子后一百六十年。距子思后亦不下百馀年。则史记所谓受业门人。似是实传。而或谓子思门人未有显名于后者。当以亲受业之说为正。此果有旁引之曲證。可破纷纭之说者耶。博雅者其各无隐。
臣对曰。孟子受业之说。 圣问中年表考證。可谓破千古之疑。开百世之惑者。则臣何敢更为赘言。而窃尝观孟子之自言。曰我私淑诸人。这私字。已非亲炙于圣人嫡传之孙之意。而这人字。尤非称道孔氏家嫡传之孙之意。则史氏所云受业子思门人之说。恐是实传。而司马贞,孔颖达之见。互相表里者也。至于孔丛子以来赵岐,王劭之论。则意谓孟子之所树立。如彼卓尔。于亲受子思之音旨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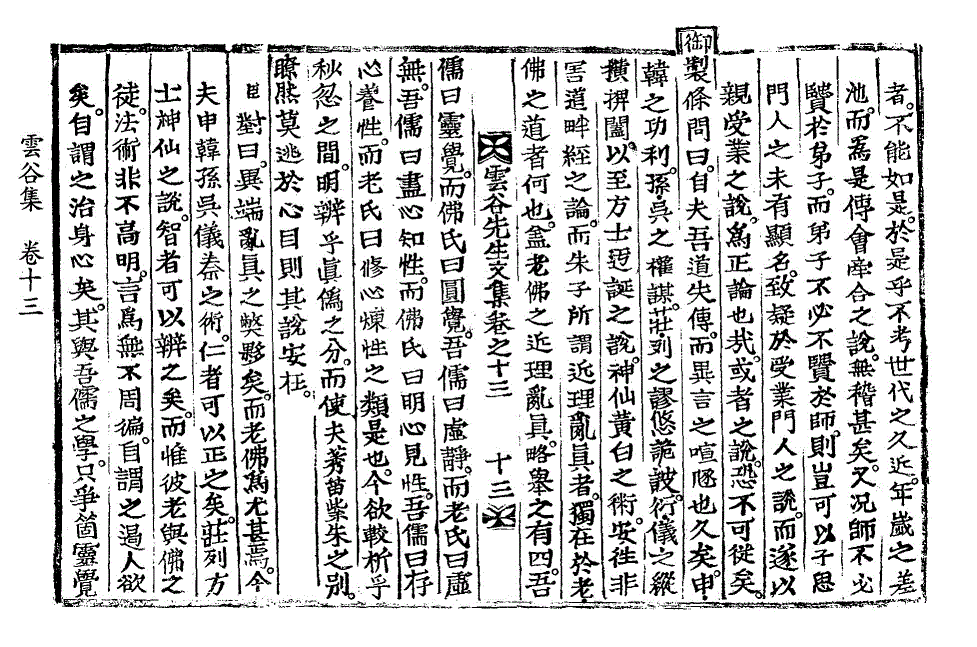 者。不能如是。于是乎不考世代之久近。年岁之差池。而为是傅会牵合之说。无稽甚矣。又况师不必贤于弟子。而弟子不必不贤于师。则岂可以子思门人之未有显名。致疑于受业门人之说。而遂以亲受业之说。为正论也哉。或者之说。恐不可从矣。
者。不能如是。于是乎不考世代之久近。年岁之差池。而为是傅会牵合之说。无稽甚矣。又况师不必贤于弟子。而弟子不必不贤于师。则岂可以子思门人之未有显名。致疑于受业门人之说。而遂以亲受业之说。为正论也哉。或者之说。恐不可从矣。御制条问曰。自夫吾道失传。而异言之喧豗也久矣。申,韩之功利。孙,吴之权谋。庄,列之谬悠诡诐。衍,仪之纵横捭阖。以至方士迂诞之说。神仙黄白之𧗱。安往非害道畔经之论。而朱子所谓近理乱真者。独在于老,佛之道者何也。盖老佛之近理乱真。略举之有四。吾儒曰灵觉。而佛氏曰圆觉。吾儒曰虚静。而老氏曰虚无。吾儒曰尽心知性。而佛氏曰明心见性。吾儒曰存心养性。而老氏曰修心炼性之类是也。今欲较析乎秒忽之间。明辨乎真伪之分。而使夫莠苗紫朱之别。瞭然莫逃于心目则其说安在。
臣对曰。异端乱真之弊夥矣。而老佛为尤甚焉。今夫申韩孙吴仪秦之术。仁者可以正之矣。庄列方士神仙之说。智者可以辨之矣。而惟彼老与佛之徒。法术非不高明。言为无不周遍。自谓之遏人欲矣。自谓之治身心矣。其与吾儒之学。只争个灵觉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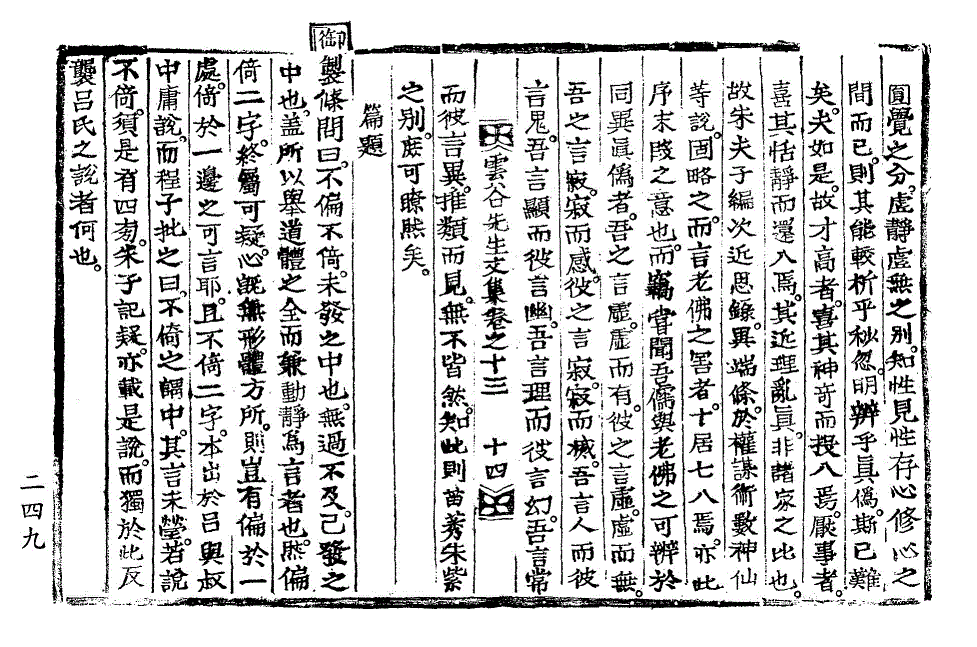 圆觉之分。虚静虚无之别。知性见性存心修心之间而已。则其能较析乎秒忽。明辨乎真伪。斯已难矣。夫如是。故才高者。喜其神奇而投入焉。厌事者。喜其恬静而还入焉。其近理乱真。非诸家之比也。故朱夫子编次近思录。异端条。于权谋术数神仙等说。固略之。而言老佛之害者。十居七八焉。亦此序末段之意也。而窃尝闻吾儒与老佛之可辨于同异真伪者。吾之言虚。虚而有。彼之言虚。虚而无。吾之言寂。寂而感。彼之言寂。寂而灭。吾言人而彼言鬼。吾言显而彼言幽。吾言理而彼言幻。吾言常而彼言异。推类而见。无不皆然。知此则苗莠朱紫之别。庶可瞭然矣。
圆觉之分。虚静虚无之别。知性见性存心修心之间而已。则其能较析乎秒忽。明辨乎真伪。斯已难矣。夫如是。故才高者。喜其神奇而投入焉。厌事者。喜其恬静而还入焉。其近理乱真。非诸家之比也。故朱夫子编次近思录。异端条。于权谋术数神仙等说。固略之。而言老佛之害者。十居七八焉。亦此序末段之意也。而窃尝闻吾儒与老佛之可辨于同异真伪者。吾之言虚。虚而有。彼之言虚。虚而无。吾之言寂。寂而感。彼之言寂。寂而灭。吾言人而彼言鬼。吾言显而彼言幽。吾言理而彼言幻。吾言常而彼言异。推类而见。无不皆然。知此则苗莠朱紫之别。庶可瞭然矣。篇题
御制条问曰。不偏不倚。未发之中也。无过不及。已发之中也。盖所以举道体之全而兼动静为言者也。然偏倚二字。终属可疑。心既无形体方所。则岂有偏于一处。倚于一边之可言耶。且不倚二字。本出于吕与叔中庸说。而程子批之曰。不倚之谓中。其言未莹。若说不倚。须是有四旁。朱子记疑。亦载是说。而独于此反袭吕氏之说者何也。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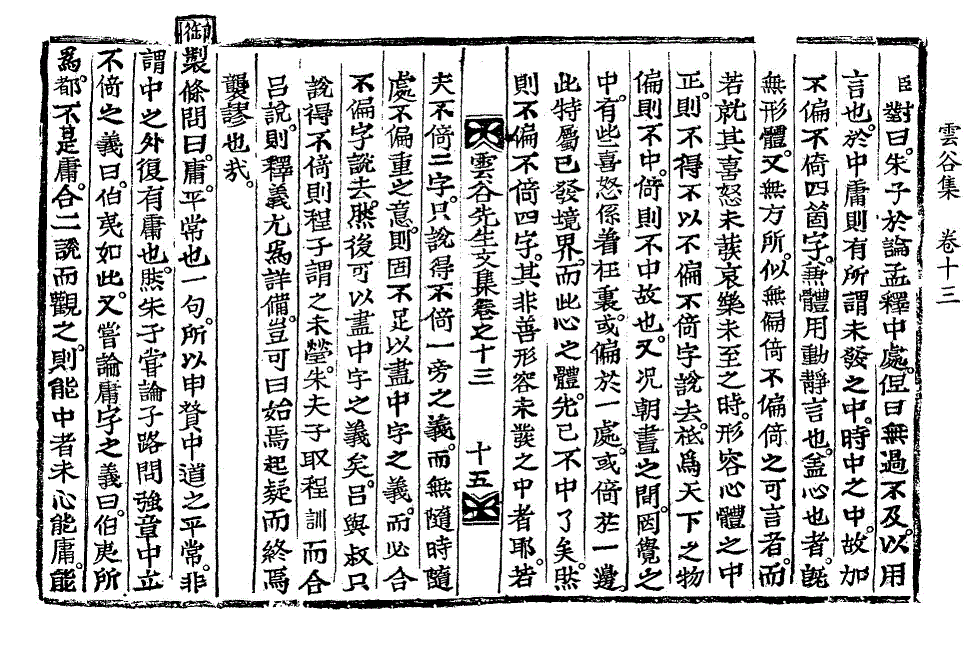 臣对曰。朱子于论孟释中处。但曰无过不及。以用言也。于中庸则有所谓未发之中。时中之中。故加不偏不倚四个字。兼体用动静言也。盖心也者。既无形体。又无方所。似无偏倚不偏倚之可言者。而若就其喜怒未发哀乐未至之时。形容心体之中正。则不得不以不偏不倚字说去。祗为天下之物偏则不中。倚则不中故也。又况朝昼之间。罔觉之中。有些喜怒系着在里。或偏于一处。或倚于一边。此特属已发境界。而此心之体。先已不中了矣。然则不偏不倚四字。其非善形容未发之中者耶。若夫不倚二字。只说得不倚一旁之义。而无随时随处不偏重之意。则固不足以尽中字之义。而必合不偏字说去。然后可以尽中字之义矣。吕与叔只说得不倚则程子谓之未莹。朱夫子取程训而合吕说。则释义尤为详备。岂可曰始焉起疑而终焉袭谬也哉。
臣对曰。朱子于论孟释中处。但曰无过不及。以用言也。于中庸则有所谓未发之中。时中之中。故加不偏不倚四个字。兼体用动静言也。盖心也者。既无形体。又无方所。似无偏倚不偏倚之可言者。而若就其喜怒未发哀乐未至之时。形容心体之中正。则不得不以不偏不倚字说去。祗为天下之物偏则不中。倚则不中故也。又况朝昼之间。罔觉之中。有些喜怒系着在里。或偏于一处。或倚于一边。此特属已发境界。而此心之体。先已不中了矣。然则不偏不倚四字。其非善形容未发之中者耶。若夫不倚二字。只说得不倚一旁之义。而无随时随处不偏重之意。则固不足以尽中字之义。而必合不偏字说去。然后可以尽中字之义矣。吕与叔只说得不倚则程子谓之未莹。朱夫子取程训而合吕说。则释义尤为详备。岂可曰始焉起疑而终焉袭谬也哉。御制条问曰。庸。平常也一句。所以申赞中道之平常。非谓中之外复有庸也。然朱子尝论子路问强章中立不倚之义曰。伯夷如此。又尝论庸字之义曰。伯夷所为。都不是庸。合二说而观之。则能中者未心能庸。能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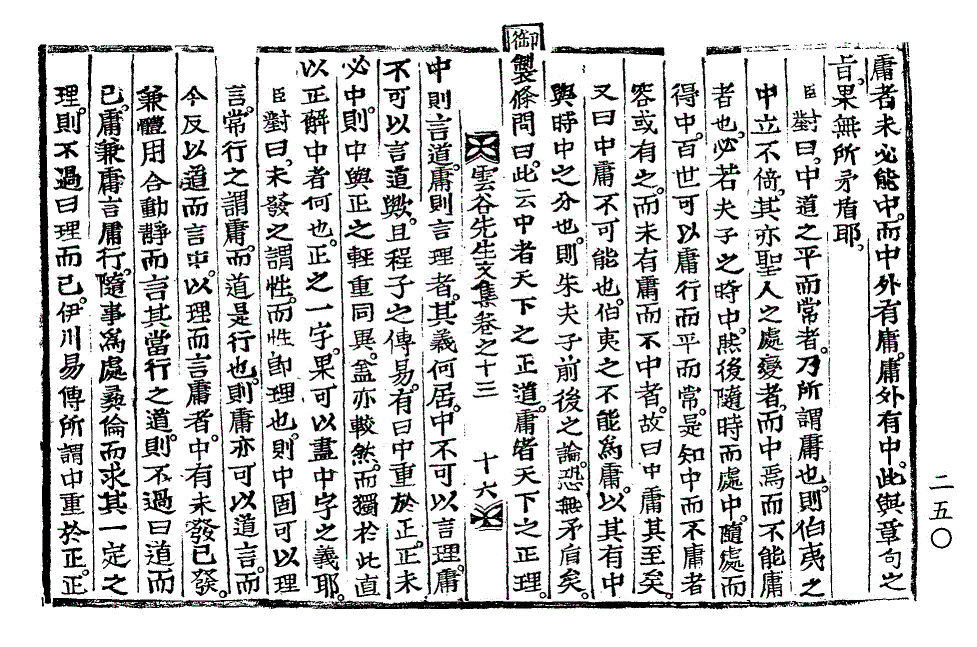 庸者未必能中。而中外有庸。庸外有中。此与章句之旨。果无所矛盾耶。
庸者未必能中。而中外有庸。庸外有中。此与章句之旨。果无所矛盾耶。臣对曰。中道之平而常者。乃所谓庸也。则伯夷之中立不倚。其亦圣人之处变者。而中焉而不能庸者也。必若夫子之时中。然后随时而处中。随处而得中。百世可以庸行而平而常。是知中而不庸者容或有之。而未有庸而不中者。故曰中庸其至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伯夷之不能为庸。以其有中与时中之分也。则朱夫子前后之论。恐无矛盾矣。
御制条问曰。此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则言道。庸则言理者。其义何居。中不可以言理。庸不可以言道欤。且程子之传易。有曰中重于正。正未必中。则中与正之轻重同异。盖亦较然。而独于此直以正解中者何也。正之一字。果可以尽中字之义耶。
臣对曰。未发之谓性。而性即理也。则中固可以理言。常行之谓庸。而道是行也。则庸亦可以道言。而今反以道而言中。以理而言庸者。中有未发已发。兼体用合动静而言其当行之道。则不过曰道而已。庸兼庸言庸行。随事为处彝伦而求其一定之理。则不过曰理而已。伊川易传所谓中重于正。正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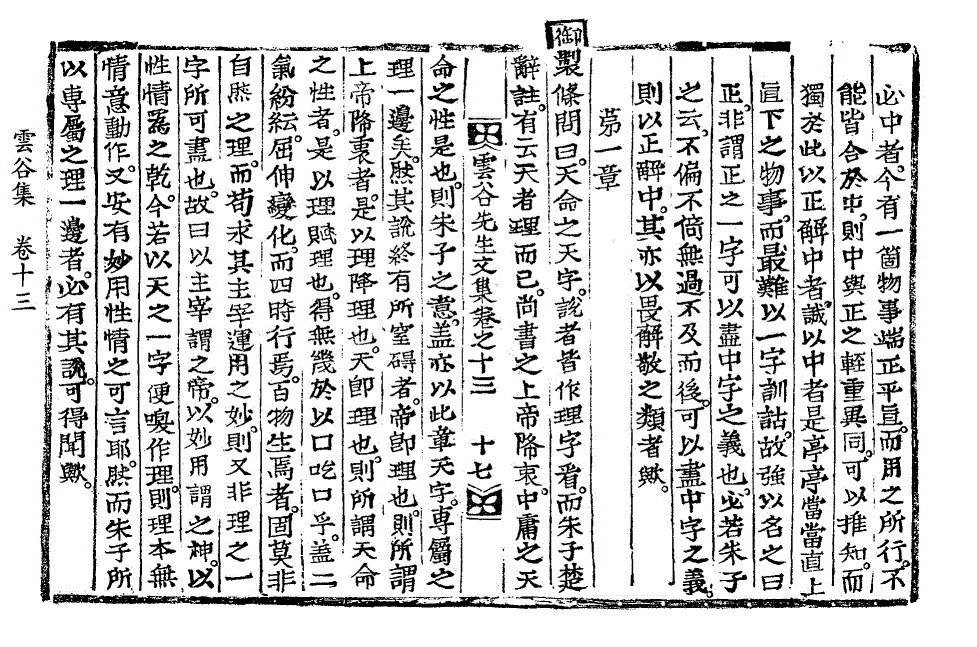 必中者。今有一个物事端正平直。而用之所行。不能皆合于中。则中与正之轻重异同。可以推知。而独于此以正解中者。诚以中者是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物事。而最难以一字训诂。故强以名之曰正。非谓正之一字可以尽中字之义也。必若朱子之云。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后。可以尽中字之义。则以正解中。其亦以畏解敬之类者欤。
必中者。今有一个物事端正平直。而用之所行。不能皆合于中。则中与正之轻重异同。可以推知。而独于此以正解中者。诚以中者是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物事。而最难以一字训诂。故强以名之曰正。非谓正之一字可以尽中字之义也。必若朱子之云。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后。可以尽中字之义。则以正解中。其亦以畏解敬之类者欤。第一章
御制条问曰。天命之天字。说者皆作理字看。而朱子楚辞注。有云天者理而已。尚书之上帝降衷。中庸之天命之性是也。则朱子之意。盖亦以此章天字。专属之理一边矣。然其说终有所窒碍者。帝即理也。则所谓上帝降衷者。是以理降理也。天即理也。则所谓天命之性者。是以理赋理也。得无几于以口吃口乎。盖二气纷纭。屈伸变化。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者。固莫非自然之理。而苟求其主宰运用之妙。则又非理之一字所可尽也。故曰以主宰谓之帝。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为之乾。今若以天之一字便唤作理。则理本无情意动作。又安有妙用性情之可言耶。然而朱子所以专属之理一边者。必有其说。可得闻欤。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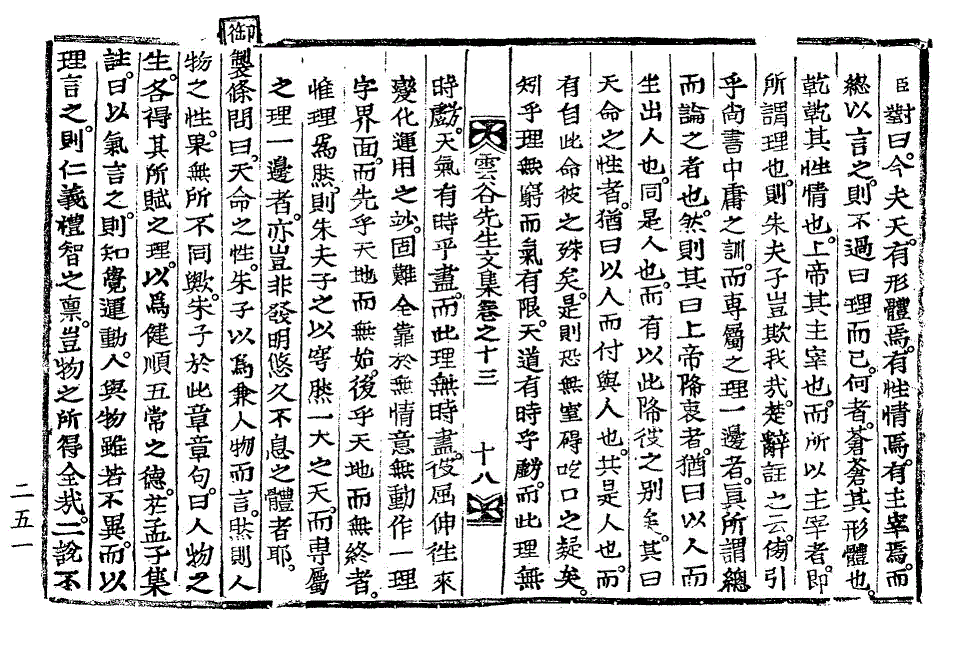 臣对曰。今夫天。有形体焉。有性情焉。有主宰焉。而总以言之。则不过曰理而已。何者。苍苍其形体也。乾乾其性情也。上帝其主宰也。而所以主宰者。即所谓理也。则朱夫子岂欺我哉。楚辞注之云。傍引乎尚书中庸之训。而专属之理一边者。真所谓总而论之者也。然则其曰上帝降衷者。犹曰以人而生出人也。同是人也。而有以此降彼之别矣。其曰天命之性者。犹曰以人而付与人也。共是人也。而有自此命彼之殊矣。是则恐无窒碍吃口之疑矣。矧乎理无穷而气有限。天道有时乎亏。而此理无时亏。天气有时乎尽。而此理无时尽。彼屈伸往来变化运用之妙。固难全靠于无情意无动作一理字界面。而先乎天地而无始。后乎天地而无终者。惟理为然。则朱夫子之以穹然一大之天。而专属之理一边者。亦岂非发明悠久不息之体者耶。
臣对曰。今夫天。有形体焉。有性情焉。有主宰焉。而总以言之。则不过曰理而已。何者。苍苍其形体也。乾乾其性情也。上帝其主宰也。而所以主宰者。即所谓理也。则朱夫子岂欺我哉。楚辞注之云。傍引乎尚书中庸之训。而专属之理一边者。真所谓总而论之者也。然则其曰上帝降衷者。犹曰以人而生出人也。同是人也。而有以此降彼之别矣。其曰天命之性者。犹曰以人而付与人也。共是人也。而有自此命彼之殊矣。是则恐无窒碍吃口之疑矣。矧乎理无穷而气有限。天道有时乎亏。而此理无时亏。天气有时乎尽。而此理无时尽。彼屈伸往来变化运用之妙。固难全靠于无情意无动作一理字界面。而先乎天地而无始。后乎天地而无终者。惟理为然。则朱夫子之以穹然一大之天。而专属之理一边者。亦岂非发明悠久不息之体者耶。御制条问曰。天命之性。朱子以为兼人物而言。然则人物之性。果无所不同欤。朱子于此章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于孟子集注。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虽若不异。而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全哉。二说不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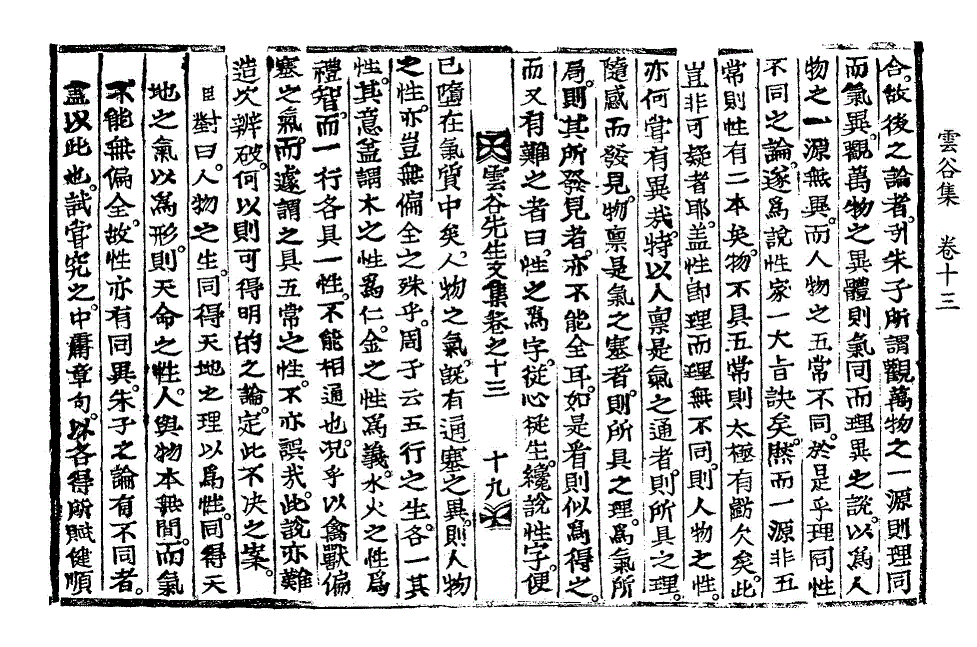 合。故后之论者。引朱子所谓观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之说。以为人物之一源无异。而人物之五常不同。于是乎理同性不同之论。遂为说性家一大旨诀矣。然而一源非五常则性有二本矣。物不具五常则太极有亏欠矣。此岂非可疑者耶。盖性即理而理无不同。则人物之性。亦何尝有异哉。特以人禀是气之通者。则所具之理。随感而发见。物禀是气之塞者。则所具之理。为气所局。则其所发见者。亦不能全耳。如是看则似为得之。而又有难之者曰。性之为字。从心从生。才说性字。便已堕在气质中矣。人物之气。既有通塞之异。则人物之性。亦岂无偏全之殊乎。周子云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意盖谓木之性为仁。金之性为义。水火之性为礼智。而一行各具一性。不能相通也。况乎以禽兽偏塞之气。而遽谓之具五常之性。不亦误哉。此说亦难造次辨破。何以则可得明的之论。定此不决之案。
合。故后之论者。引朱子所谓观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之说。以为人物之一源无异。而人物之五常不同。于是乎理同性不同之论。遂为说性家一大旨诀矣。然而一源非五常则性有二本矣。物不具五常则太极有亏欠矣。此岂非可疑者耶。盖性即理而理无不同。则人物之性。亦何尝有异哉。特以人禀是气之通者。则所具之理。随感而发见。物禀是气之塞者。则所具之理。为气所局。则其所发见者。亦不能全耳。如是看则似为得之。而又有难之者曰。性之为字。从心从生。才说性字。便已堕在气质中矣。人物之气。既有通塞之异。则人物之性。亦岂无偏全之殊乎。周子云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意盖谓木之性为仁。金之性为义。水火之性为礼智。而一行各具一性。不能相通也。况乎以禽兽偏塞之气。而遽谓之具五常之性。不亦误哉。此说亦难造次辨破。何以则可得明的之论。定此不决之案。臣对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则天命之性。人与物本无间。而气不能无偏全。故性亦有同异。朱子之论有不同者。盖以此也。试尝究之。中庸章句。以各得所赋健顺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2L 页
 五常之德言之者。是释天命之性。而从万物一源上说也。孟子集注。以仁义礼智物岂得全等语言之者。是释生之谓性。而就万物异体上说也。论其方赋之初。莫不具是理。故人物之一源无异。看其禀得之后。理为气所掩。故人物之五常不同。则理同气异。气同理异之训。正为朱子盛水不漏处。李文纯尝有言曰。论万物之一源则物物之中。莫不有天命本然之性。观万物之异体则物之偏塞。不得具健顺五常之德。此可谓互相发明。或者引程子才说性。周子各一其性之语。以为性亦有偏全。而物不具五常。则不惟不识理气之同异。其于此章天命之性。已看得不透矣。又何足辨破也。
五常之德言之者。是释天命之性。而从万物一源上说也。孟子集注。以仁义礼智物岂得全等语言之者。是释生之谓性。而就万物异体上说也。论其方赋之初。莫不具是理。故人物之一源无异。看其禀得之后。理为气所掩。故人物之五常不同。则理同气异。气同理异之训。正为朱子盛水不漏处。李文纯尝有言曰。论万物之一源则物物之中。莫不有天命本然之性。观万物之异体则物之偏塞。不得具健顺五常之德。此可谓互相发明。或者引程子才说性。周子各一其性之语。以为性亦有偏全。而物不具五常。则不惟不识理气之同异。其于此章天命之性。已看得不透矣。又何足辨破也。御制条问曰。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又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又曰。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数句之内。三言各字。而不嫌其重复者何也。或谓各之为言。即各异之意。于此政可见人物五常之不同。或谓各之为言。即莫不皆然之意。于此政可见人物五常之无异。玆两说者。孰得朱子之本旨也。
臣对曰。章句释字之例。有字叠而义不叠者。有字同而旨不同者。试以章句内三各字观之。先儒曰。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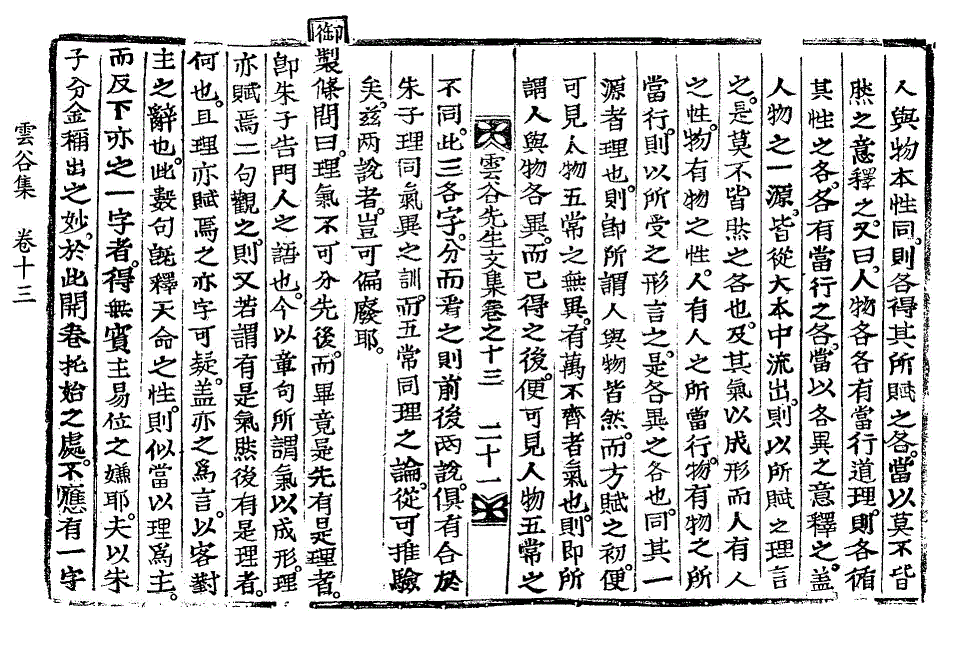 人与物本性同。则各得其所赋之各。当以莫不皆然之意释之。又曰。人物各各有当行道理。则各循其性之各。各有当行之各。当以各异之意释之。盖人物之一源。皆从大本中流出。则以所赋之理言之。是莫不皆然之各也。及其气以成形而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人有人之所当行。物有物之所当行。则以所受之形言之。是各异之各也。同其一源者理也。则即所谓人与物皆然。而方赋之初。便可见人物五常之无异。有万不齐者气也。则即所谓人与物各异。而已得之后。便可见人物五常之不同。此三各字。分而看之则前后两说。俱有合于朱子理同气异之训。而五常同理之论。从可推验矣。玆两说者。岂可偏废耶。
人与物本性同。则各得其所赋之各。当以莫不皆然之意释之。又曰。人物各各有当行道理。则各循其性之各。各有当行之各。当以各异之意释之。盖人物之一源。皆从大本中流出。则以所赋之理言之。是莫不皆然之各也。及其气以成形而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人有人之所当行。物有物之所当行。则以所受之形言之。是各异之各也。同其一源者理也。则即所谓人与物皆然。而方赋之初。便可见人物五常之无异。有万不齐者气也。则即所谓人与物各异。而已得之后。便可见人物五常之不同。此三各字。分而看之则前后两说。俱有合于朱子理同气异之训。而五常同理之论。从可推验矣。玆两说者。岂可偏废耶。御制条问曰。理气不可分先后。而毕竟是先有是理者。即朱子告门人之语也。今以章句所谓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二句观之。则又若谓有是气然后有是理者。何也。且理亦赋焉之亦字可疑。盖亦之为言。以客对主之辞也。此数句既释天命之性。则似当以理为主。而反下亦之一字者。得无宾主易位之嫌耶。夫以朱子分金称出之妙。于此开卷托始之处。不应有一字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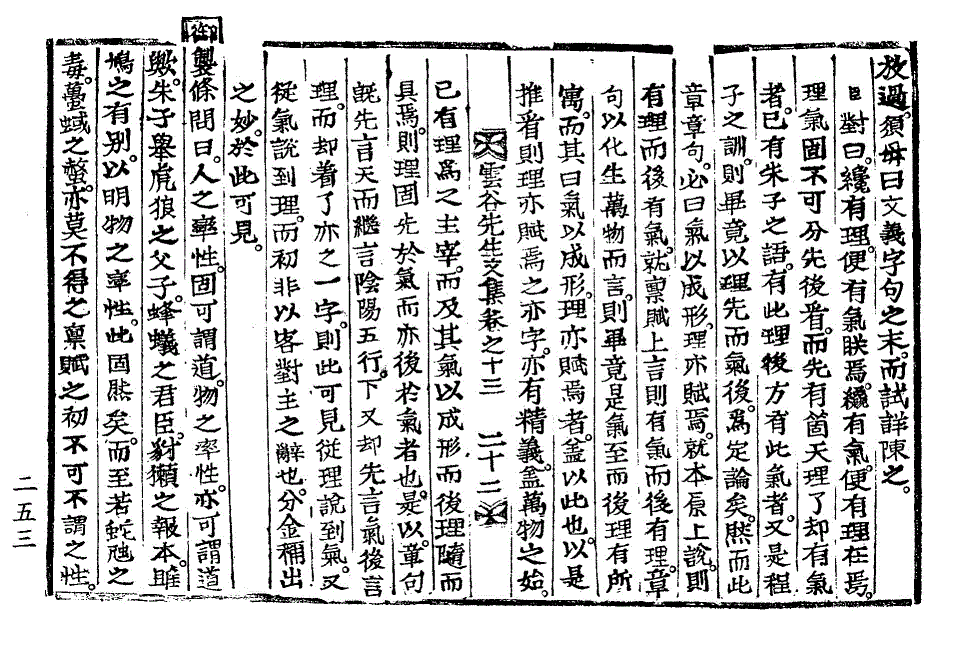 放过。须毋曰文义字句之末。而试详陈之。
放过。须毋曰文义字句之末。而试详陈之。臣对曰。才有理。便有气眹焉。才有气。便有理在焉。理气固不可分先后看。而先有个天理了却有气者。已有朱子之语。有此理后方有此气者。又是程子之训。则毕竟以理先而气后。为定论矣。然而此章章句。必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就本原上说。则有理而后有气。就禀赋上言则有气而后有理。章句以化生万物而言。则毕竟是气至而后理有所寓。而其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者。盖以此也。以是推看则理亦赋焉之亦字。亦有精义。盖万物之始。已有理为之主宰。而及其气以成形而后理随而具焉。则理固先于气而亦后于气者也。是以。章句既先言天而继言阴阳五行。下又却先言气后言理。而却着了亦之一字。则此可见从理说到气。又从气说到理。而初非以客对主之辞也。分金称出之妙。于此可见。
御制条问曰。人之率性。固可谓道。物之率性。亦可谓道欤。朱子举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以明物之率性。此固然矣。而至若蛇虺之毒。虿蜮之螫。亦莫不得之禀赋之初不可不谓之性。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4H 页
 则率是性者。皆可谓之道耶。先儒又以牛之可耕。马之可乘。鸡之司晨。犬之司夜。为物之率性。是数者。本然欤。气质欤。若以为气质则有违于此章言性之旨。若以为本然则是直以知觉运动为本然之性。果何异于释氏作用是性之说耶。
则率是性者。皆可谓之道耶。先儒又以牛之可耕。马之可乘。鸡之司晨。犬之司夜。为物之率性。是数者。本然欤。气质欤。若以为气质则有违于此章言性之旨。若以为本然则是直以知觉运动为本然之性。果何异于释氏作用是性之说耶。臣对曰。按语类曰。率性之谓道。通人物而言。盖自人而言之。则循其仁义礼智之性而为人之道。自物而言之。则循其飞潜动植之性而为物之道。各循其性之自然者。莫非个道也。是以。朱夫子特举虎狼之仁。蜂蚁之义。豺獭之孝。雎鸠之别。以明物之率性。则这所谓物各有当行之道。而至若蛇虺蜂虿之有毒螫。亦是禀赋上得来。则斯固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然而性之恶者。是固气禀之攸为。而初非本然底理。则率是性者。又安可谓之道耶。真西山尝以虎狼之搏噬。牛马之踶躅为非道。则尤可见蛇虺蜂虿之着不得道字矣。至于牛可耕马可乘鸡之司晨犬之司夜。先儒引之以为率性。而语类。以牛之性马之性。谓各循其理之自然。则程子所谓在物为理。在人为性是也。然则这性字。当属之本然一边。而谓之理。则其有合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4L 页
 于章句言性之旨。谓之自然。则其亦异乎释氏作用是性之说矣。
于章句言性之旨。谓之自然。则其亦异乎释氏作用是性之说矣。御制条问曰。昔程子论杨子云学所以修性之语曰。杨雄不识性。盖性本纯粹至善之理。固无待于用力修治。而修性之说。有似乎杞柳杯棬之论也。然则此章所谓修道之教者。又何以称焉。道可以言修。性不可以言修。则性与道。果若是不同。而明道性即道之说。非也欤。
臣对曰。性是自然之理。尧舜性之。汤武反之。则修之一字。着了不得。是以。吾儒有尽性养性之目。而修性之论。独发于杨子。则宜程子之所深斥也。盖性是纯乎理者也。当循其自然而已。更无事乎用力而修治。则修性之说。其不几于宋人之揠苗耶。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过者修之而使之无过。不及者修之而使之无不及。则其于日用当行之间。不得无品节裁制之工。而修之一字。阙却他不得者也。然则性与道固无异。而性是纯乎理者。则不容有品节之工。道是率其性者。则不可无修为之方。岂可以道可以言修。性不可以言修。有疑于程子性即道之训。而反去道外寻性。性外寻道耶。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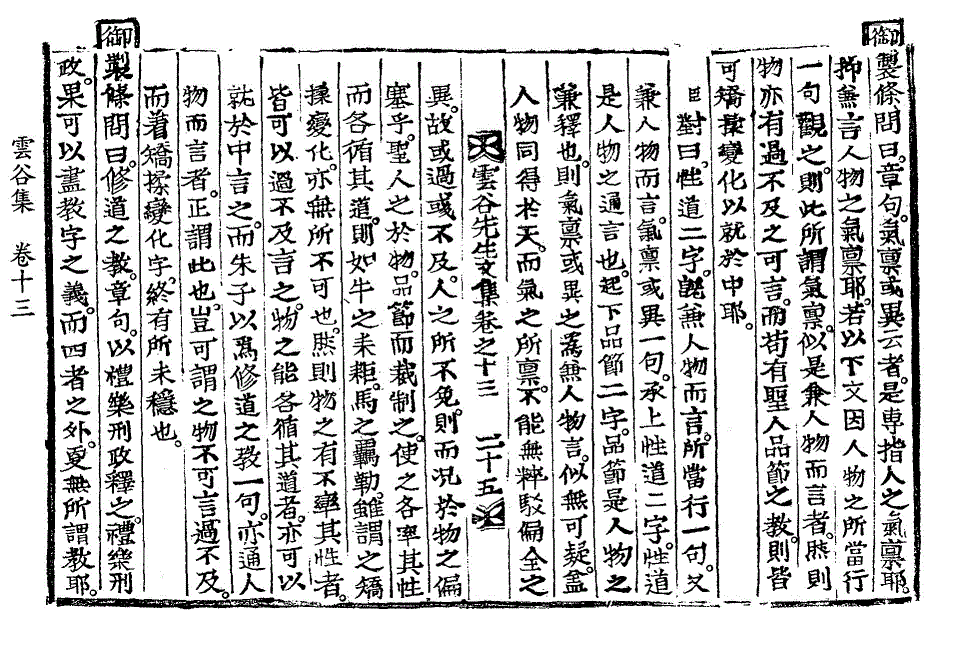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章句。气禀或异云者。是专指人之气禀耶。抑兼言人物之气禀耶。若以下文因人物之所当行一句观之。则此所谓气禀。似是兼人物而言者。然则物亦有过不及之可言。而苟有圣人品节之教。则皆可矫揉变化以就于中耶。
御制条问曰。章句。气禀或异云者。是专指人之气禀耶。抑兼言人物之气禀耶。若以下文因人物之所当行一句观之。则此所谓气禀。似是兼人物而言者。然则物亦有过不及之可言。而苟有圣人品节之教。则皆可矫揉变化以就于中耶。臣对曰。性道二字。既兼人物而言。所当行一句。又兼人物而言。气禀或异一句。承上性道二字。性道是人物之通言也。起下品节二字。品节是人物之兼释也。则气禀或异之为兼人物言。似无可疑。盖人物同得于天。而气之所禀。不能无粹驳偏全之异。故或过或不及。人之所不免。则而况于物之偏塞乎。圣人之于物。品节而裁制之。使之各率其性而各循其道。则如牛之耒耟。马之羁勒。虽谓之矫揉变化。亦无所不可也。然则物之有不率其性者。皆可以过不及言之。物之能各循其道者。亦可以就于中言之。而朱子以为修道之教一句。亦通人物而言者。正谓此也。岂可谓之物不可言过不及。而着矫揉变化字。终有所未稳也。
御制条问曰。修道之教。章句。以礼乐刑政释之。礼乐刑政。果可以尽教字之义。而四者之外。更无所谓教耶。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5L 页
 盖圣人之言教。必先曰渐以仁。摩以义。使民日迁善不知而已。至于礼乐刑政制度文为。则特不过济教之具耳。较诸作兴动绥之妙。自有内外本末之分。而朱子之直以四者为教。更不言向上第一义者。何也。
盖圣人之言教。必先曰渐以仁。摩以义。使民日迁善不知而已。至于礼乐刑政制度文为。则特不过济教之具耳。较诸作兴动绥之妙。自有内外本末之分。而朱子之直以四者为教。更不言向上第一义者。何也。臣对曰。臣尝闻修道之教。专为气禀之偏而设。盖以人物之生。不能无过不及。而圣人为之品节防范。以为法于天下。则必须礼乐刑政以齐一之。然后方可以就于中而无过不及之差矣。章句之直以礼乐刑政。释修道之教者。盖以此也。且况礼乐刑政。特济教之具。圣人之教。必待是四者而行焉。如舜之命九官。周之设六卿。要不出礼乐刑政之外。而教化之隆。非后世所及。则渐摩成就之道。盖寓于四者之中。而作兴动绥之妙。尽在于是矣。是以。朱夫子于或问。以仁义礼智四个。备言修道之教。而于此直以四者为训解。诚以礼乐是中和之教。刑政又所以弼教。而中和位育。无非推此功效。则岂可曰制度文为之末。而更不言向上第一义耶。
御制条问曰。章句。人知己之有性以下数句。有今旧本之异。旧本云。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6H 页
 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是其说之文达理顺。亦何逊于今本。而朱子之不慊旧本。必改其说者。何故也。旧本之不可不改。今本之不容有阙。可详言欤。
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是其说之文达理顺。亦何逊于今本。而朱子之不慊旧本。必改其说者。何故也。旧本之不可不改。今本之不容有阙。可详言欤。臣对曰。章句旧本之说。骤看了。虽若无损于今本。而细究其旨。似不若今本之尤精密。旧本云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则虽其发明一源之理。极尽无馀蕴。而以人道教三字。分作三段说去。似涉于人自人道自道教自教之嫌。而今本则就性上说天。就道上说性。就教上说道。直与子思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一串贯来。而教之因乎道。道之由乎性。性之出于天。条理贯通。脉络昭然则就看今旧二本。恐不无浅深疏密之别。朱子之必以今本为定者。实为晚年定论。而后儒之一遵今本。不亦宜乎。
御制条问曰。性道教三者。即一篇之纲领。而第二节。独以道之一字。郑重引起者何也。或谓戒慎恐惧。即由教而入者。故道也者一句。紧承上文修道之教而言。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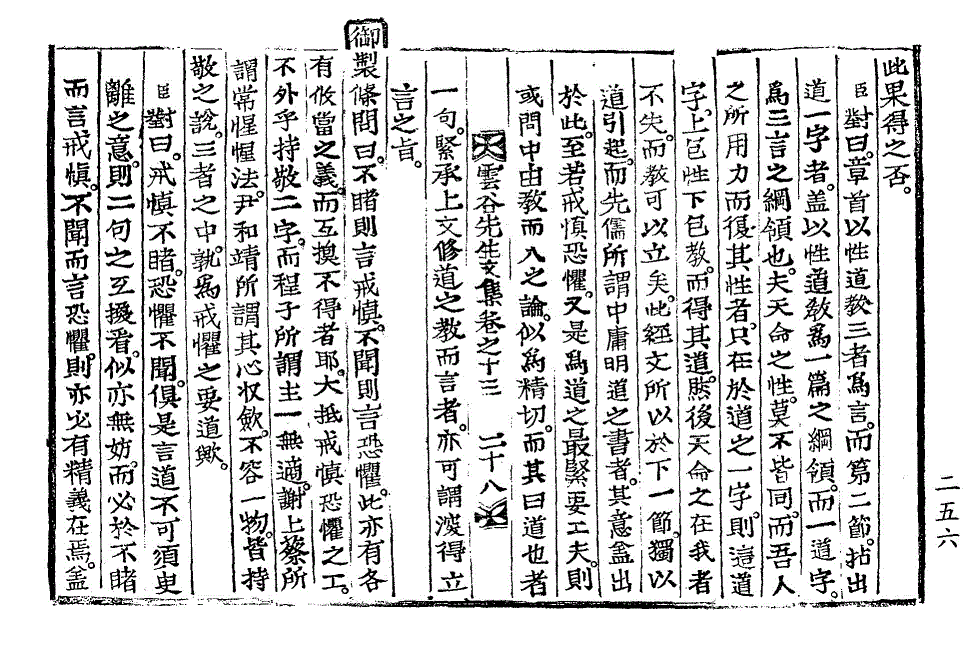 此果得之否。
此果得之否。臣对曰。章首以性道教三者为言。而第二节。拈出道一字者。盖以性道教为一篇之纲领。而一道字。为三言之纲领也。夫天命之性。莫不皆同。而吾人之所用力而复其性者。只在于道之一字。则这道字。上包性下包教。而得其道。然后天命之在我者不失。而教可以立矣。此经文所以于下一节。独以道引起。而先儒所谓中庸明道之书者。其意盖出于此。至若戒慎恐惧。又是为道之最紧要工夫。则或问中由教而入之论。似为精切。而其曰道也者一句。紧承上文修道之教而言者。亦可谓深得立言之旨。
御制条问曰。不睹则言戒慎。不闻则言恐惧。此亦有各有攸当之义。而互换不得者耶。大抵戒慎恐惧之工。不外乎持敬二字。而程子所谓主一无适。谢上蔡所谓常惺惺法。尹和靖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皆持敬之说。三者之中。孰为戒惧之要道欤。
臣对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俱是言道不可须臾离之意。则二句之互换看。似亦无妨。而必于不睹而言戒慎。不闻而言恐惧。则亦必有精义在焉。盖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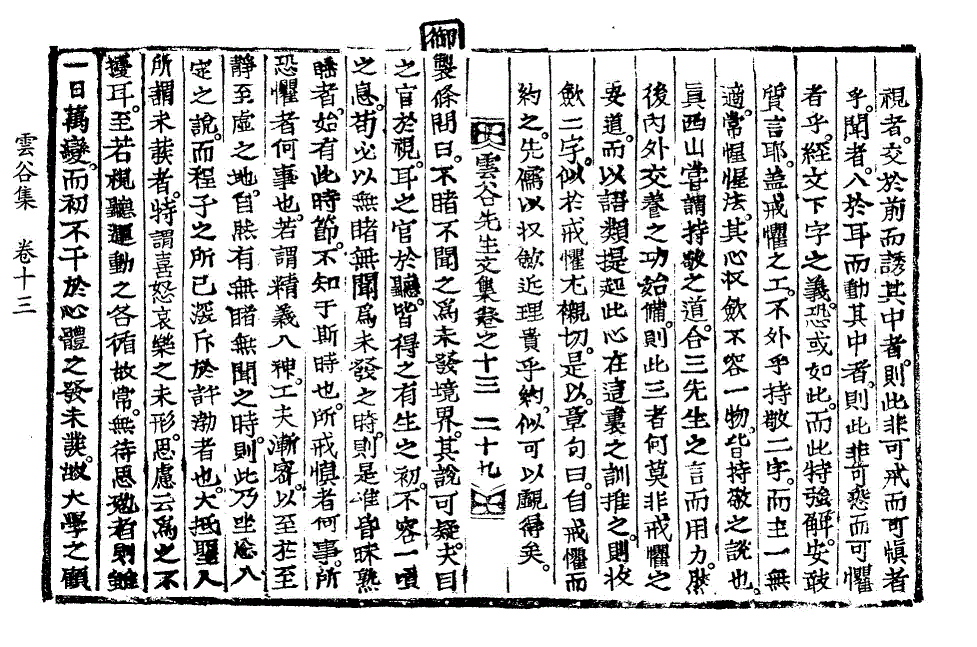 视者。交于前而诱其中者。则此非可戒而可慎者乎。闻者。入于耳而动其中者。则此非可恐而可惧者乎。经文下字之义。恐或如此。而此特强解。安敢质言耶。盖戒惧之工。不外乎持敬二字。而主一无适。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皆持敬之说也。真西山尝谓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然后内外交养之功始备。则此三者何莫非戒惧之要道。而以语类提起此心在这里之训推之。则收敛二字。似于戒惧尤衬切。是以。章句曰。自戒惧而约之。先儒以收敛近理贵乎约。似可以觑得矣。
视者。交于前而诱其中者。则此非可戒而可慎者乎。闻者。入于耳而动其中者。则此非可恐而可惧者乎。经文下字之义。恐或如此。而此特强解。安敢质言耶。盖戒惧之工。不外乎持敬二字。而主一无适。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皆持敬之说也。真西山尝谓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然后内外交养之功始备。则此三者何莫非戒惧之要道。而以语类提起此心在这里之训推之。则收敛二字。似于戒惧尤衬切。是以。章句曰。自戒惧而约之。先儒以收敛近理贵乎约。似可以觑得矣。御制条问曰。不睹不闻之为未发境界。其说可疑。夫目之官于视。耳之官于听。皆得之有生之初。不容一顷之息。苟必以无睹无闻为未发之时。则是唯昏昧熟睡者。始有此时节。不知于斯时也。所戒慎者何事。所恐惧者何事也。若谓精义入神。工夫渐密。以至于至静至虚之地。自然有无睹无闻之时。则此乃坐忘入定之说。而程子之所已深斥于许渤者也。大抵圣人所谓未发者。特谓喜怒哀乐之未形。思虑云为之不扰耳。至若视听运动之各循故常。无待思勉者则虽一日万变。而初不干于心体之发未发。故大学之顾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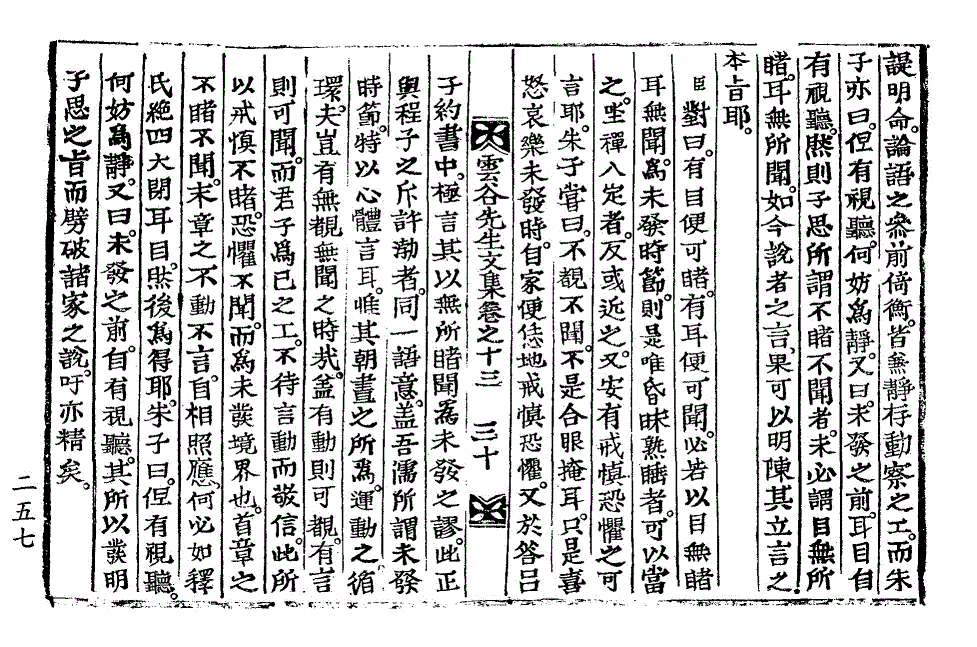 諟明命。论语之参前倚衡。皆兼静存动察之工。而朱子亦曰。但有视听。何妨为静。又曰。未发之前。耳目自有视听。然则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未必谓目无所睹。耳无所闻。如今说者之言。果可以明陈其立言之本旨耶。
諟明命。论语之参前倚衡。皆兼静存动察之工。而朱子亦曰。但有视听。何妨为静。又曰。未发之前。耳目自有视听。然则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未必谓目无所睹。耳无所闻。如今说者之言。果可以明陈其立言之本旨耶。臣对曰。有目便可睹。有耳便可闻。必若以目无睹耳无闻。为未发时节。则是唯昏昧熟睡者。可以当之。坐禅入定者。反或近之。又安有戒慎恐惧之可言耶。朱子尝曰。不睹不闻。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乐未发时。自家便恁地戒慎恐惧。又于答吕子约书中。极言其以无所睹闻为未发之谬。此正与程子之斥许渤者。同一语意。盖吾儒所谓未发时节。特以心体言耳。惟其朝昼之所为。运动之循环。夫岂有无睹无闻之时哉。盖有动则可睹。有言则可闻。而君子为己之工。不待言动而敬信。此所以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为未发境界也。首章之不睹不闻。末章之不动不言。自相照应。何必如释氏绝四大闭耳目。然后为得耶。朱子曰。但有视听。何妨为静。又曰。未发之前。自有视听。其所以发明子思之旨而劈破诸家之说。吁亦精矣。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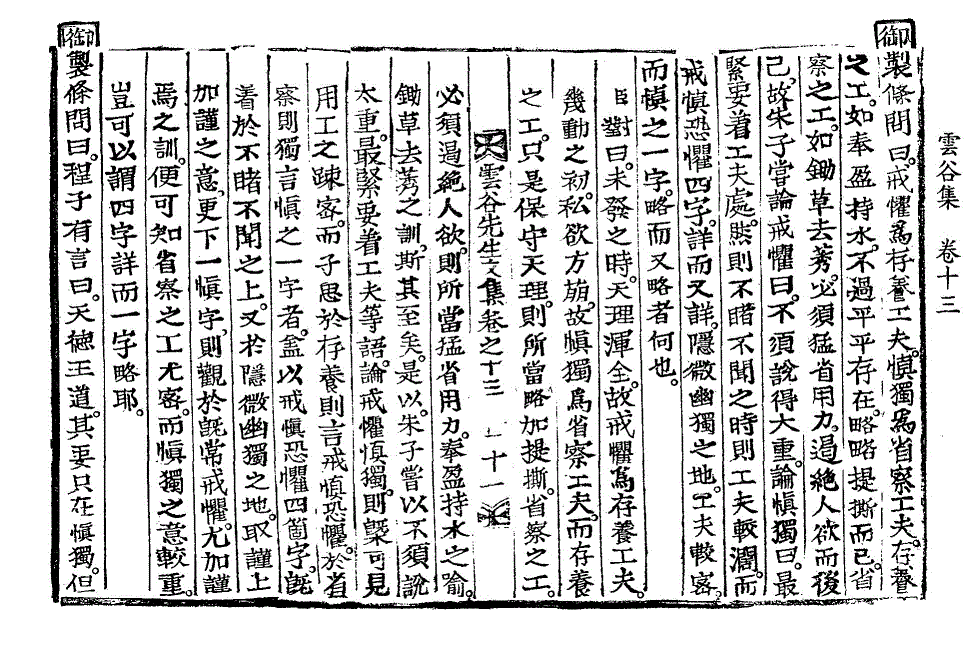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戒惧为存养工夫。慎独为省察工夫。存养之工。如奉盈持水。不过平平存在。略略提撕而已。省察之工。如锄草去莠。必须猛省用力。遏绝人欲而后已。故朱子尝论戒惧曰。不须说得大重。论慎独曰。最紧要着工夫处。然则不睹不闻之时则工夫较阔。而戒慎恐惧四字。详而又详。隐微幽独之地。工夫较密。而慎之一字。略而又略者何也。
御制条问曰。戒惧为存养工夫。慎独为省察工夫。存养之工。如奉盈持水。不过平平存在。略略提撕而已。省察之工。如锄草去莠。必须猛省用力。遏绝人欲而后已。故朱子尝论戒惧曰。不须说得大重。论慎独曰。最紧要着工夫处。然则不睹不闻之时则工夫较阔。而戒慎恐惧四字。详而又详。隐微幽独之地。工夫较密。而慎之一字。略而又略者何也。臣对曰。未发之时。天理浑全。故戒惧为存养工夫。几动之初。私欲方萌。故慎独为省察工夫。而存养之工。只是保守天理。则所当略加提撕。省察之工。必须遏绝人欲。则所当猛省用力。奉盈持水之喻。锄草去莠之训。斯其至矣。是以。朱子尝以不须说太重。最紧要着工夫等语。论戒惧慎独。则槩可见用工之疏密。而子思于存养则言戒慎恐惧。于省察则独言慎之一字者。盖以戒慎恐惧四个字。既着于不睹不闻之上。又于隐微幽独之地。取谨上加谨之意。更下一慎字。则观于既常戒惧。尤加谨焉之训。便可知省察之工尤密。而慎独之意较重。岂可以谓四字详而一字略耶。
御制条问曰。程子有言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独。但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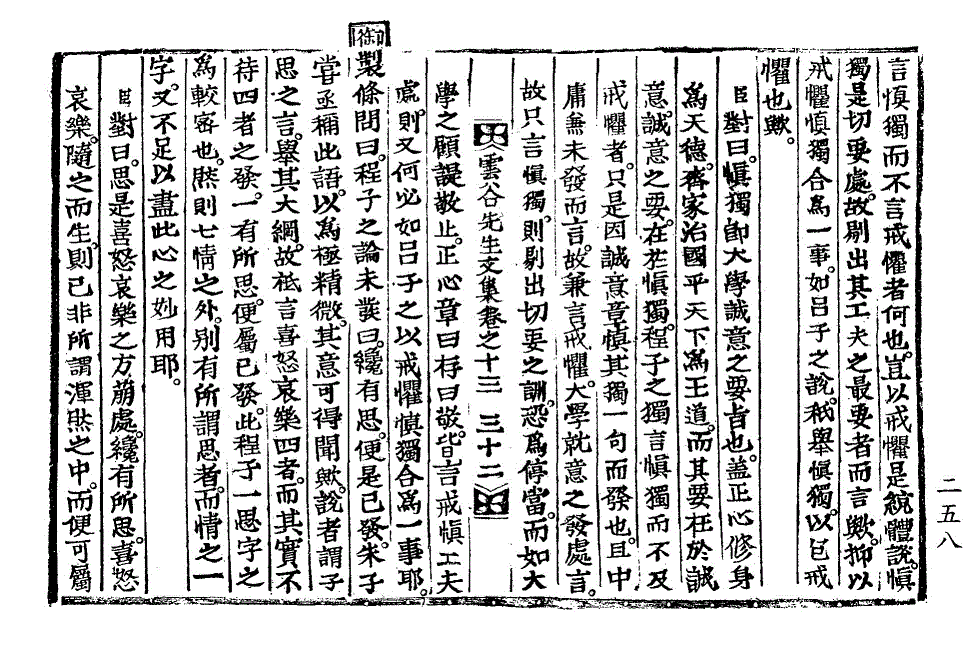 言慎独而不言戒惧者何也。岂以戒惧是统体说。慎独是切要处。故剔出其工夫之最要者而言欤。抑以戒惧慎独合为一事。如吕子之说。秖举慎独。以包戒惧也欤。
言慎独而不言戒惧者何也。岂以戒惧是统体说。慎独是切要处。故剔出其工夫之最要者而言欤。抑以戒惧慎独合为一事。如吕子之说。秖举慎独。以包戒惧也欤。臣对曰。慎独即大学诚意之要旨也。盖正心修身为天德。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王道。而其要在于诚意。诚意之要。在于慎独。程子之独言慎独而不及戒惧者。只是因诚意章慎其独一句而发也。且中庸兼未发而言。故兼言戒惧。大学就意之发处言。故只言慎独。则剔出切要之训。恐为停当。而如大学之顾諟敬止。正心章曰存曰敬。皆言戒慎工夫处。则又何必如吕子之以戒惧慎独合为一事耶。
御制条问曰。程子之论未发曰。才有思。便是已发。朱子尝亟称此语。以为极精微。其意可得闻欤。说者谓子思之言。举其大纲。故祗言喜怒哀乐四者。而其实不待四者之发。一有所思。便属已发。此程子一思字之为较密也。然则七情之外。别有所谓思者。而情之一字。又不足以尽此心之妙用耶。
臣对曰。思是喜怒哀乐之方萌处。才有所思。喜怒哀乐。随之而生。则已非所谓浑然之中。而便可属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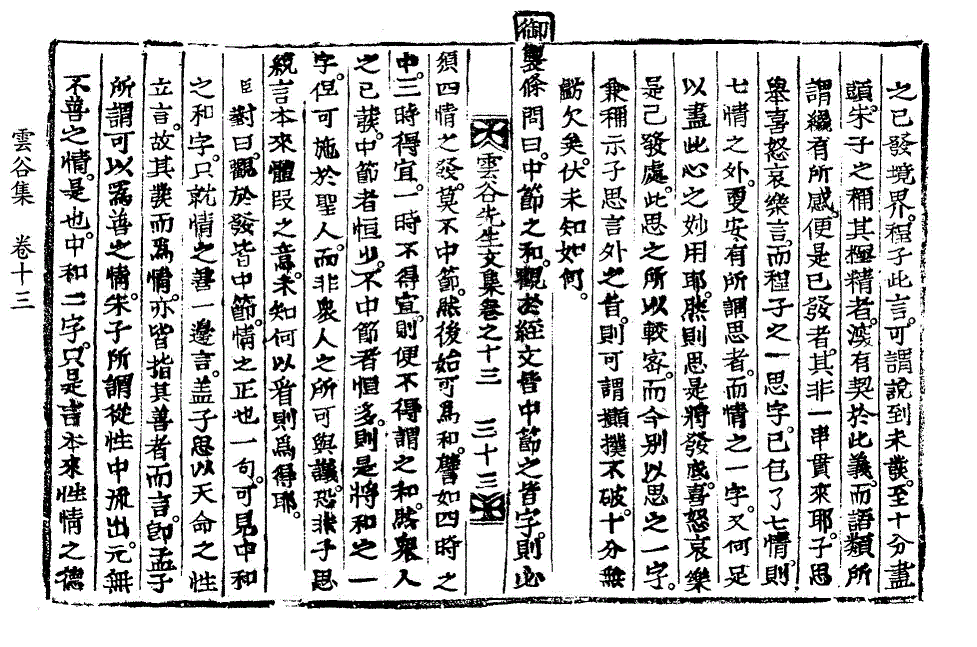 之已发境界。程子此言。可谓说到未发。至十分尽头。朱子之称其极精者。深有契于此义。而语类所谓才有所感。便是已发者。其非一串贯来耶。子思举喜怒哀乐言。而程子之一思字。已包了七情。则七情之外。更安有所谓思者。而情之一字。又何足以尽此心之妙用耶。然则思是将发底。喜怒哀乐是已发处。此思之所以较密。而今别以思之一字。兼称示子思言外之旨。则可谓攧扑不破。十分无亏欠矣。伏未知如何。
之已发境界。程子此言。可谓说到未发。至十分尽头。朱子之称其极精者。深有契于此义。而语类所谓才有所感。便是已发者。其非一串贯来耶。子思举喜怒哀乐言。而程子之一思字。已包了七情。则七情之外。更安有所谓思者。而情之一字。又何足以尽此心之妙用耶。然则思是将发底。喜怒哀乐是已发处。此思之所以较密。而今别以思之一字。兼称示子思言外之旨。则可谓攧扑不破。十分无亏欠矣。伏未知如何。御制条问曰。中节之和。观于经文皆中节之皆字。则必须四情之发。莫不中节。然后始可为和。譬如四时之中。三时得宜。一时不得宜。则便不得谓之和。然众人之已发。中节者恒少。不中节者恒多。则是将和之一字。但可施于圣人。而非众人之所可与议。恐非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意。未知何以看则为得耶。
臣对曰。观于发皆中节。情之正也一句。可见中和之和字。只就情之善一边言。盖子思以天命之性立言。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即孟子所谓可以为善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中和二字。只是言本来性情之德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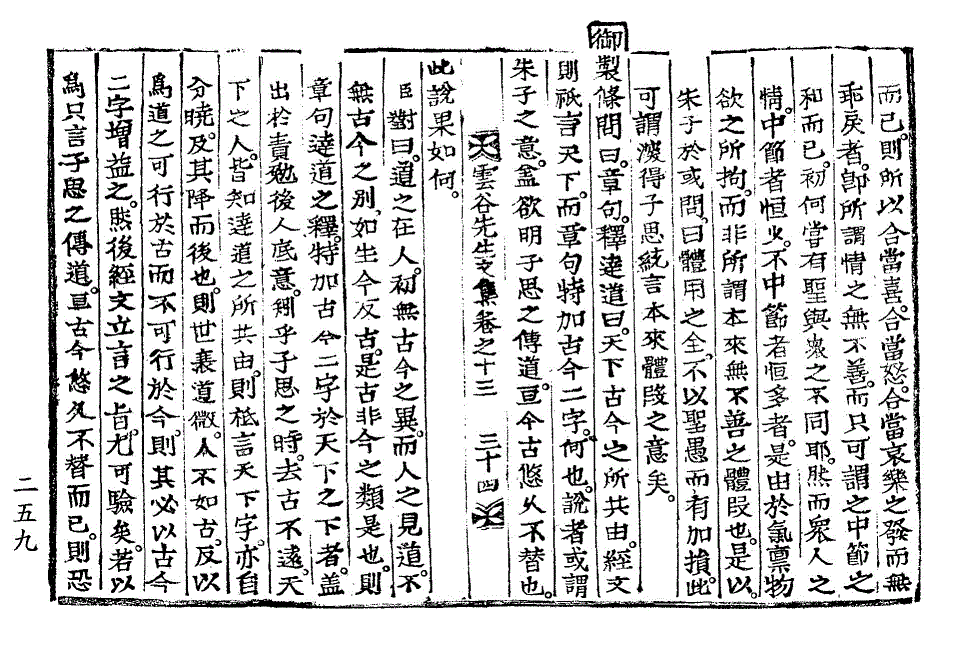 而已。则所以合当喜。合当怒。合当哀乐之发而无乖戾者。即所谓情之无不善。而只可谓之中节之和而已。初何尝有圣与众之不同耶。然而众人之情。中节者恒少。不中节者恒多者。是由于气禀物欲之所拘。而非所谓本来无不善之体段也。是以。朱子于或问。曰体用之全。不以圣愚而有加损。此可谓深得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意矣。
而已。则所以合当喜。合当怒。合当哀乐之发而无乖戾者。即所谓情之无不善。而只可谓之中节之和而已。初何尝有圣与众之不同耶。然而众人之情。中节者恒少。不中节者恒多者。是由于气禀物欲之所拘。而非所谓本来无不善之体段也。是以。朱子于或问。曰体用之全。不以圣愚而有加损。此可谓深得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意矣。御制条问曰。章句。释达道曰。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经文则祇言天下。而章句特加古今二字。何也。说者或谓朱子之意。盖欲明子思之传道。亘今古悠久不替也。此说果如何。
臣对曰。道之在人。初无古今之异。而人之见道。不无古今之别。如生今反古。是古非今之类是也。则章句达道之释。特加古今二字于天下之下者。盖出于责勉后人底意。矧乎子思之时。去古不远。天下之人。皆知达道之所共由。则祗言天下字。亦自分晓。及其降而后也。则世衰道微。人不如古。反以为道之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则其必以古今二字增益之。然后经文立言之旨。尤可验矣。若以为只言子思之传道。亘古今悠久不替而已。则恐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0H 页
 有渗漏之病矣。
有渗漏之病矣。御制条问曰。致中和之致。与致曲之致。致知之致不同。盖中和即至善之异名。本无待于人之付畀增益。则又何可致之有哉。特以常人之心不知所以存之。则天理昧而大本不立。故必致戒惧之功。以复其本然之中而已。非中有所未尽而推致之。如致曲致知之谓也。然朱子语类。论中和之义曰。略略地中和。亦可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尝以中贴中垛中红心之说。喻致中之义。据此则朱子之意。似若谓中有分数。而必待人之推致者。何也。
臣对曰。中和是言性情之德。而致之一字。是在人底工夫。则非如致知致曲之知有所未尽。气不能无偏。而推以致之之谓也。盖天命之性。浑然在中。而中和之体段已具。则吾人性分之内。只有个纯粹至善之理而已。然而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则中有所倚着而大本不立矣。动而不知所以察之。则反有所乖戾而达道不行矣。是以。自戒惧而约之。由外收敛以尽乎内。而极其中之至。自谨独而精之。自内省察以尽乎外。而极其和之至。则这致字。不过因其本然之中而做到精密纯熟极尽之谓。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0L 页
 曷尝谓中有所未尽而有待于人之推致耶。朱子尝有略略地中和。要得十分中和等语。此正与语类所谓如煖閤人皆以火炉为中。且去火炉寻个至中处方是的当之语。而又尝有中贴中垛中红心之喻。则特以中之者之工有致与未致。而若其红心之中。固自在也。岂可以前后两说。遽谓之中有分数。而反疑推而极之之训耶。
曷尝谓中有所未尽而有待于人之推致耶。朱子尝有略略地中和。要得十分中和等语。此正与语类所谓如煖閤人皆以火炉为中。且去火炉寻个至中处方是的当之语。而又尝有中贴中垛中红心之喻。则特以中之者之工有致与未致。而若其红心之中。固自在也。岂可以前后两说。遽谓之中有分数。而反疑推而极之之训耶。御制条问曰。章句。自戒惧而约之一句。解之者有二说。或谓自其有睹有闻之时。已用戒慎恐惧之工。而渐约之以至于不睹不闻之时。或谓戒惧工夫虽本通贯动静。而此所谓戒惧。既与谨独对言。则当专属之静一边。盖戒惧是静时工夫之始。而工夫自有浅深。故必约之。然后可以至于无所偏倚之极工也。二说孰为正解也。
臣对曰。按语类曰。戒谨恐惧。不睹不闻。是从见闻处。戒谨恐惧。到那不睹不闻处。以是推之则前说似得。而今以自戒惧而约之一句观之。约之一字。是从戒慎恐惧上约之又约。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之谓。则朱夫子盖以静之终。动之始。截为两段。而以戒惧谨独。分属之中和者也。添一约字。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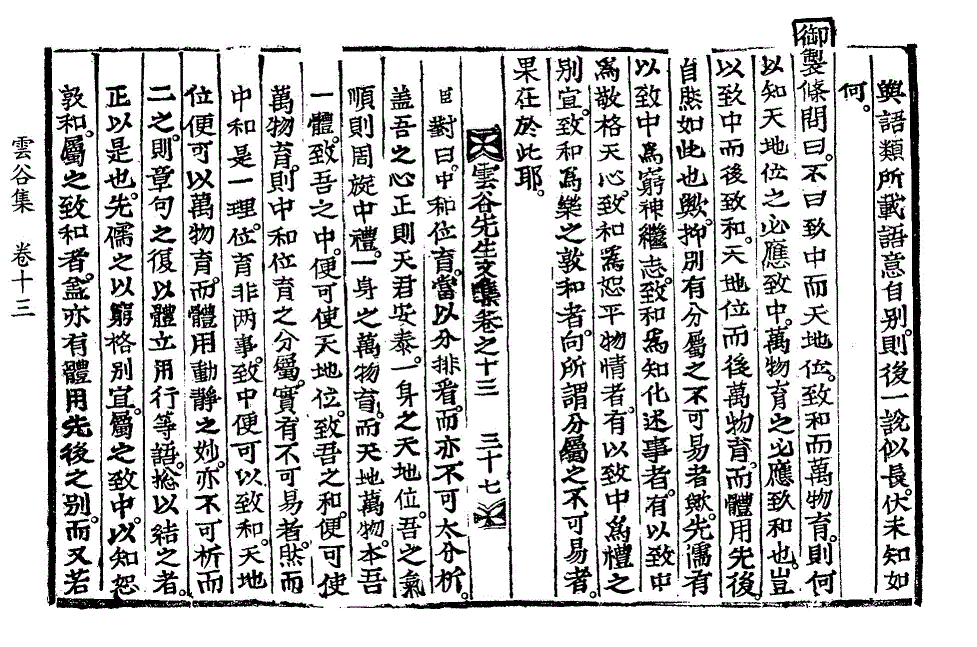 与语类所载语意自别。则后一说似长。伏未知如何。
与语类所载语意自别。则后一说似长。伏未知如何。御制条问曰。不曰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万物育。则何以知天地位之必应致中。万物育之必应致和也。岂以致中而后致和。天地位而后万物育。而体用先后。自然如此也欤。抑别有分属之不可易者欤。先儒有以致中为穷神继志。致和为知化述事者。有以致中为敬格天心。致和为恕平物情者。有以致中为礼之别宜。致和为乐之敦和者。向所谓分属之不可易者。果在于此耶。
臣对曰。中和位育。当以分排看。而亦不可太分析。盖吾之心正则天君安泰。一身之天地位。吾之气顺则周旋中礼。一身之万物育。而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致吾之中。便可使天地位。致吾之和。便可使万物育。则中和位育之分属。实有不可易者。然而中和是一理。位育非两事。致中便可以致和。天地位便可以万物育。而体用动静之妙。亦不可析而二之。则章句之复以体立用行等语。总以结之者。正以是也。先儒之以穷格别宜。属之致中。以知恕敦和。属之致和者。盖亦有体用先后之别。而又若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1L 页
 专主于分开说。则恐未免分裂之患矣。
专主于分开说。则恐未免分裂之患矣。御制条问曰。章句。学问之极功一句。以致中和言。圣人之能事一句。以位育言欤。抑极功与能事。并指位育之事欤。若谓分属于中和位育。则此二句。既承上文所谓效验如此之下。不应于此更言工夫。若谓并指位育之事。则又未免叠床架屋。何以看则为得耶。
臣对曰。极功能事。不必分属于中和位育。亦不必谓并指位育之事。窃观此二句。统承上文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而言。则似当以吾之心正气顺。为学问之极工。以天地之心正气顺。为圣人之能事。如此看似无大谬。而此特臆断强解。安敢曰信然也。
御制条问曰。观圣人之书。必观其首章。盖以开卷托始。作家所慎。而一书所言。莫不原本于此也。试以此书言之。则诚为道学之枢纽。故至诚明诚。屡致意焉。而首章则不少概见。致知为入德之门户。故学问思辨。言之重复。而首章则未尝说道者。何也。是必有不言之中。意实包在者。可得闻欤。
臣对曰。诚只实理而已。天以实理而为性命之原。人得实理于是心而有道教之名。则首章性道教三言。已包得这个诚字。而篇内所谓至诚之尽其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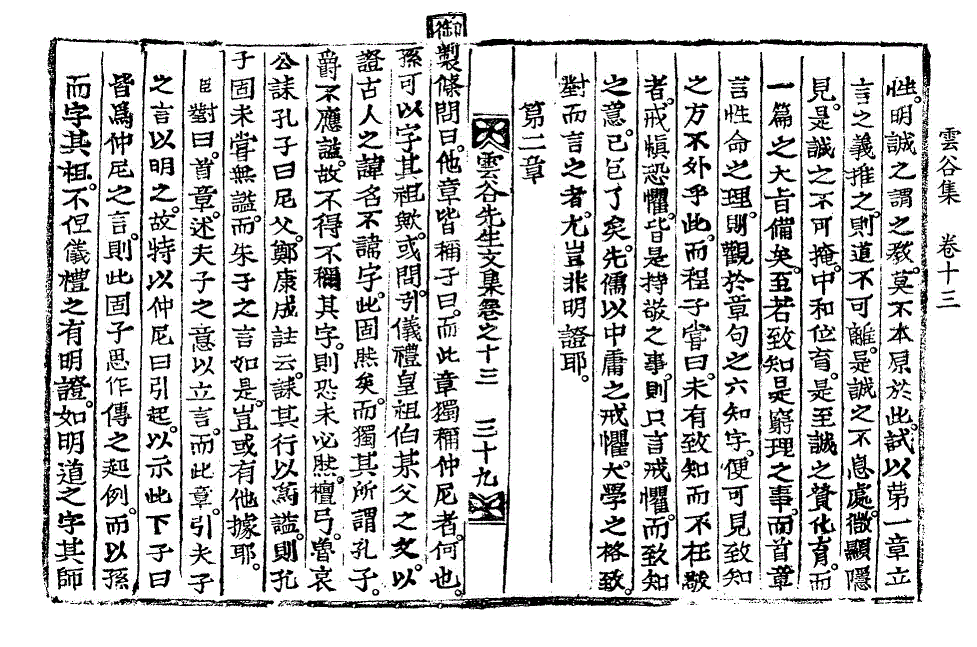 性。明诚之谓之教。莫不本原于此。试以第一章立言之义推之。则道不可离。是诚之不息处。微显隐见。是诚之不可掩。中和位育。是至诚之赞化育。而一篇之大旨备矣。至若致知是穷理之事。而首章言性命之理。则观于章句之六知字。便可见致知之方不外乎此。而程子尝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戒慎恐惧。皆是持敬之事。则只言戒惧。而致知之意。已包了矣。先儒以中庸之戒惧。大学之格致。对而言之者。尤岂非明證耶。
性。明诚之谓之教。莫不本原于此。试以第一章立言之义推之。则道不可离。是诚之不息处。微显隐见。是诚之不可掩。中和位育。是至诚之赞化育。而一篇之大旨备矣。至若致知是穷理之事。而首章言性命之理。则观于章句之六知字。便可见致知之方不外乎此。而程子尝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戒慎恐惧。皆是持敬之事。则只言戒惧。而致知之意。已包了矣。先儒以中庸之戒惧。大学之格致。对而言之者。尤岂非明證耶。第二章
御制条问曰。他章皆称子曰。而此章独称仲尼者。何也。孙可以字其祖欤。或问。引仪礼皇祖伯某父之文。以證古人之讳名不讳字。此固然矣。而独其所谓孔子。爵不应谥。故不得不称其字。则恐未必然。檀弓。鲁哀公诔孔子曰尼父。郑康成注云。诔其行以为谥。则孔子固未尝无谥。而朱子之言如是。岂或有他据耶。
臣对曰。首章。述夫子之意以立言。而此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故特以仲尼曰引起。以示此下子曰皆为仲尼之言。则此固子思作传之起例。而以孙而字其祖。不但仪礼之有明證。如明道之字其师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2L 页
 曰茂叔。伊川之字其兄曰伯淳。则古人之不讳字。在宋时犹然。此固无疑。而或问爵不应谥之训。亦有所据。今按郊特牲注。云殷大夫以上有谥。周制。虽命士不谥。则况于夫子而谥之乎。哀公诔孔子而未闻其加之谥。则尼父云者。盖是尊称之辞。古人称字。有亶父显父之称。则尼父之称。毕竟是称字之义。而其实仲尼与尼父无别也。郑氏谓诔其行以为谥。则无或指其尊称之辞。看作易名之义者乎。或问之證益信。而郑注之失自见矣。
曰茂叔。伊川之字其兄曰伯淳。则古人之不讳字。在宋时犹然。此固无疑。而或问爵不应谥之训。亦有所据。今按郊特牲注。云殷大夫以上有谥。周制。虽命士不谥。则况于夫子而谥之乎。哀公诔孔子而未闻其加之谥。则尼父云者。盖是尊称之辞。古人称字。有亶父显父之称。则尼父之称。毕竟是称字之义。而其实仲尼与尼父无别也。郑氏谓诔其行以为谥。则无或指其尊称之辞。看作易名之义者乎。或问之證益信。而郑注之失自见矣。御制条问曰。首章专言理。此章兼言气质。盖君子小人之分。专由于气质之不同。而此章既以君子小人对言。则其不可谓专言本然之理也明矣。或云此章之君子小人。秖言敬肆之分而未及乎气质。至第四章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然后始言气质。故章句所谓生禀之异者。在第四章而不在此章。此其说似矣。而但君子之所以敬。小人之所以肆。究其所由。不外乎气质之不同。则穷本探原之论。不得不以此章为兼言气质。未知如何。
臣对曰。君子小人之分。亶在于气质之不同。则不待敬肆之间。而其生禀已是有别。是以。下文君子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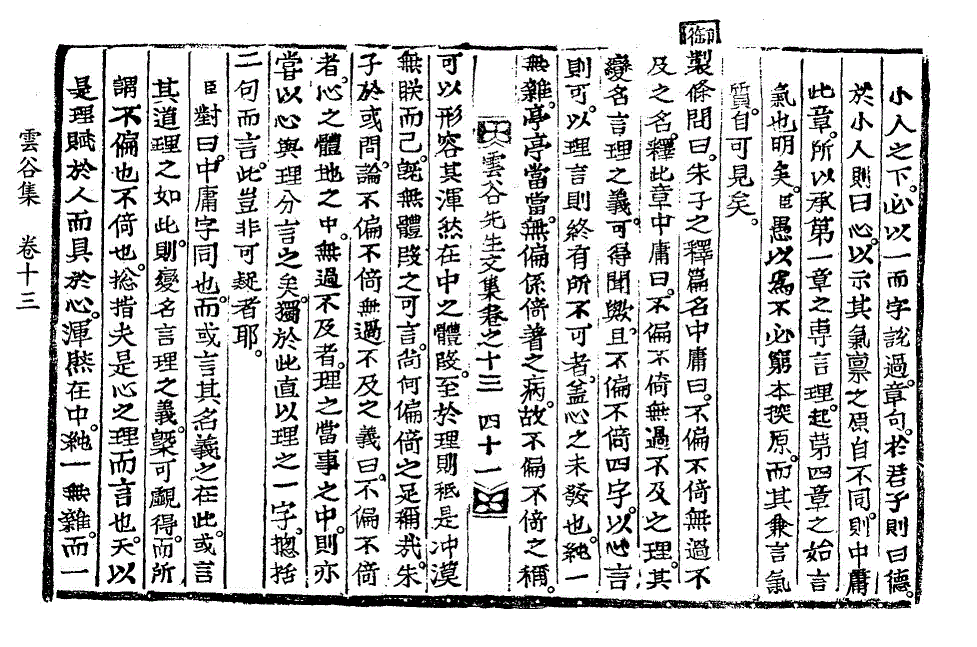 小人之下。必以一而字说过。章句。于君子则曰德。于小人则曰心。以示其气禀之原自不同。则中庸此章。所以承第一章之专言理。起第四章之始言气也明矣。臣愚以为不必穷本探原。而其兼言气质。自可见矣。
小人之下。必以一而字说过。章句。于君子则曰德。于小人则曰心。以示其气禀之原自不同。则中庸此章。所以承第一章之专言理。起第四章之始言气也明矣。臣愚以为不必穷本探原。而其兼言气质。自可见矣。御制条问曰。朱子之释篇名中庸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释此章中庸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理。其变名言理之义。可得闻欤。且不偏不倚四字。以心言则可。以理言则终有所不可者。盖心之未发也。纯一无杂。亭亭当当。无偏系倚着之病。故不偏不倚之称。可以形容其浑然在中之体段。至于理则秪是冲漠无眹而已。既无体段之可言。尚何偏倚之足称哉。朱子于或问。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曰。不偏不倚者。心之体地之中。无过不及者。理之当事之中。则亦尝以心与理分言之矣。独于此直以理之一字。总括二句而言。此岂非可疑者耶。
臣对曰。中庸字同也。而或言其名义之在此。或言其道理之如此。则变名言理之义。槩可觑得。而所谓不偏也不倚也。总指夫是心之理而言也。天以是理赋于人而具于心。浑然在中。纯一无杂。而一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3L 页
 有偏倚。此理便有亏欠矣。是以。朱夫子于或问。以心与理分而言之。而其下乃曰。方其未发。虽未有无过不及之可名。而所以为无过不及之本体。实在于是云尔。则其未发也理为之主。已发也理为之用。而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大抵皆理也。是理之外焉有所谓心耶。
有偏倚。此理便有亏欠矣。是以。朱夫子于或问。以心与理分而言之。而其下乃曰。方其未发。虽未有无过不及之可名。而所以为无过不及之本体。实在于是云尔。则其未发也理为之主。已发也理为之用。而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大抵皆理也。是理之外焉有所谓心耶。御制条问曰。时中之时。以程子禹稷颜子之喻。朱子尧舜禅受之说观之。则意自分晓。盖此时字。如孟子所谓圣之时。子思所谓时措之时。即经权通变。各适其时之谓也。是以。章句曰。随时而处中。又曰。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此正时中之正解。而至于下文。复云戒慎恐惧无时不中。则却似以时中。为须臾不离道之义者。何也。且时中即已发之中。戒惧即未发时工夫。而朱子之合而言之者。其义安在。
臣对曰。时中之时。已带来须臾不离之义。而究其源。则只当以未发之中为本。窃考朱子之言。曰中庸之中。大旨在时中上。若推其本则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为时中之中。又曰。能时中者。盖有那未发之中在。然则时中之中。分明是戒慎恐惧中得来。而所谓大本立而达道行也。尧之钦若。舜之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4H 页
 兢业。禹之日孜。颜之好学。无非所以做出他时中之道。而以至孟子所谓圣之时。子思所谓时措者。何莫非这个道理耶。而况本章有小人反中庸。小人无忌惮之训。则戒慎恐惧之为中。本文已发之矣。岂朱子之创言耶。
兢业。禹之日孜。颜之好学。无非所以做出他时中之道。而以至孟子所谓圣之时。子思所谓时措者。何莫非这个道理耶。而况本章有小人反中庸。小人无忌惮之训。则戒慎恐惧之为中。本文已发之矣。岂朱子之创言耶。御制条问曰。说者皆以此章上下二节。并作孔子之言。盖因首章总注。有其下十章。子思引孔子之言之文也。然以经文反覆潜玩。则上一节。政与论语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辞意相似。而至于下一节则不过申释上文之馀意而已。圣人之言。净洁简奥。不应自言而自释其意。似当以上一节为孔子之言。下一节为子思之言。未知如何。
臣对曰。此章下一节。为子思之言。蔡氏亦有是说。而试以朱子意考之。不但首章总注言之。至二十八章。先引孔子之言。次有子思之训。而朱子以此以下子思之言。逐条分别之。则何独于此章不然。而李文纯亦谓君子之中庸以下。朱子亦以为孔子之言。故不云子思之言。此可谓深得章句之旨。盖此篇首章。即子思所述。此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释首章之义。则不应于此一节。反解夫子之
云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4L 页
 言。朱子之训。无乃有见于是。而所谓自言而自释。则圣人之言。虽甚简奥。亦自明切。如大学之经一章。中庸之九经章。反覆言之。而无非所以引起其端。辨说其事。则后儒之以蔡说为误者。似或不为无据矣。
言。朱子之训。无乃有见于是。而所谓自言而自释。则圣人之言。虽甚简奥。亦自明切。如大学之经一章。中庸之九经章。反覆言之。而无非所以引起其端。辨说其事。则后儒之以蔡说为误者。似或不为无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