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x 页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序]
[序]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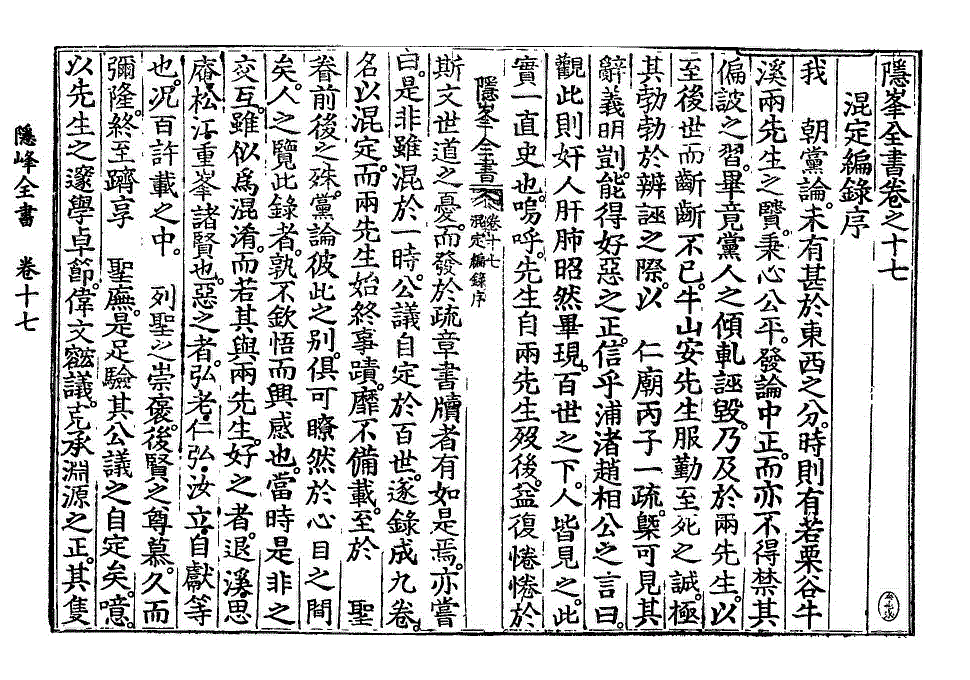 混定编录序[宋焕箕]
混定编录序[宋焕箕]我 朝党论。未有甚于东西之分。时则有若栗谷牛溪两先生之贤。秉心公平。发论中正。而亦不得禁其偏诐之习。毕竟党人之倾轧诬毁。乃及于两先生。以至后世而龂龂不已。牛山安先生服勤至死之诚。极其勃勃于辨诬之际。以 仁庙丙子一疏。槩可见其辞义明剀。能得好恶之正。信乎浦渚赵相公之言曰。观此则奸人肝肺昭然毕现。百世之下。人皆见之。此实一直史也。呜呼。先生自两先生殁后。益复惓惓于斯文世道之忧。而发于疏章书牍者有如是焉。亦尝曰。是非虽混于一时。公议自定于百世。遂录成九卷。名以混定。而两先生始终事迹。靡不备载。至于 圣眷前后之殊。党论彼此之别。俱可瞭然于心目之间矣。人之览此录者。孰不钦悟而兴感也。当时是非之交互。虽似为混淆。而若其与两先生。好之者。退溪,思庵,松江,重峰诸贤也。恶之者。弘老,仁弘,汝立,自献等也。况百许载之中。 列圣之崇褒。后贤之尊慕。久而弥隆。终至跻享 圣庑。是足验其公议之自定矣。噫。以先生之邃学卓节。伟文宏容议。克承渊源之正。其只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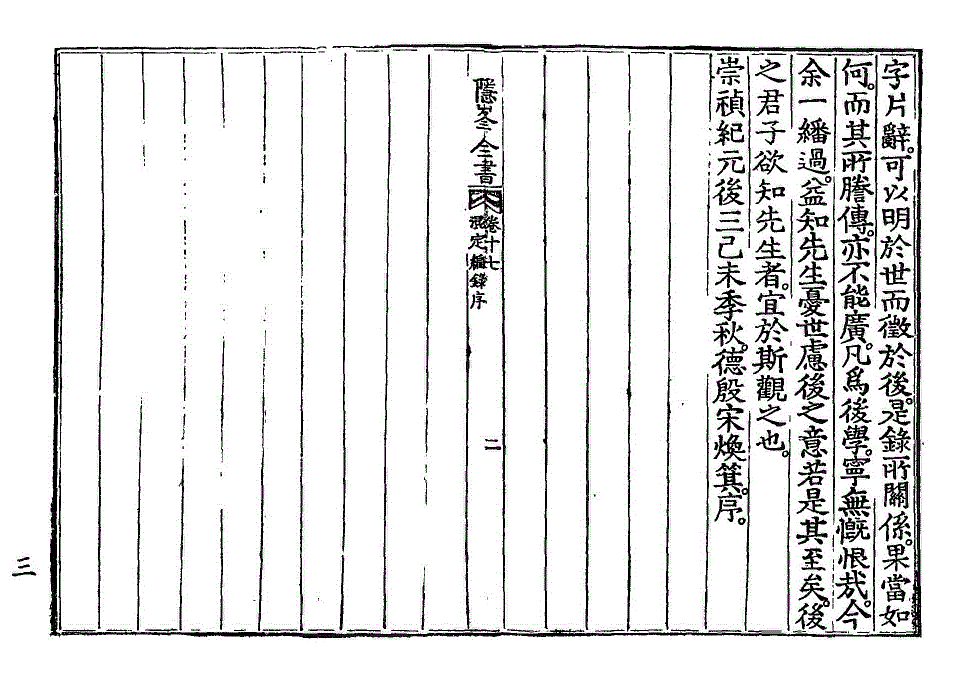 字片辞。可以明于世而徵于后。是录所关系。果当如何。而其所誊传。亦不能广。凡为后学。宁无慨恨哉。今余一翻过。益知先生忧世虑后之意若是其至矣。后之君子欲知先生者。宜于斯观之也。
字片辞。可以明于世而徵于后。是录所关系。果当如何。而其所誊传。亦不能广。凡为后学。宁无慨恨哉。今余一翻过。益知先生忧世虑后之意若是其至矣。后之君子欲知先生者。宜于斯观之也。崇祯纪元后三己未季秋。德殷宋焕箕。序。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混定编录(前集)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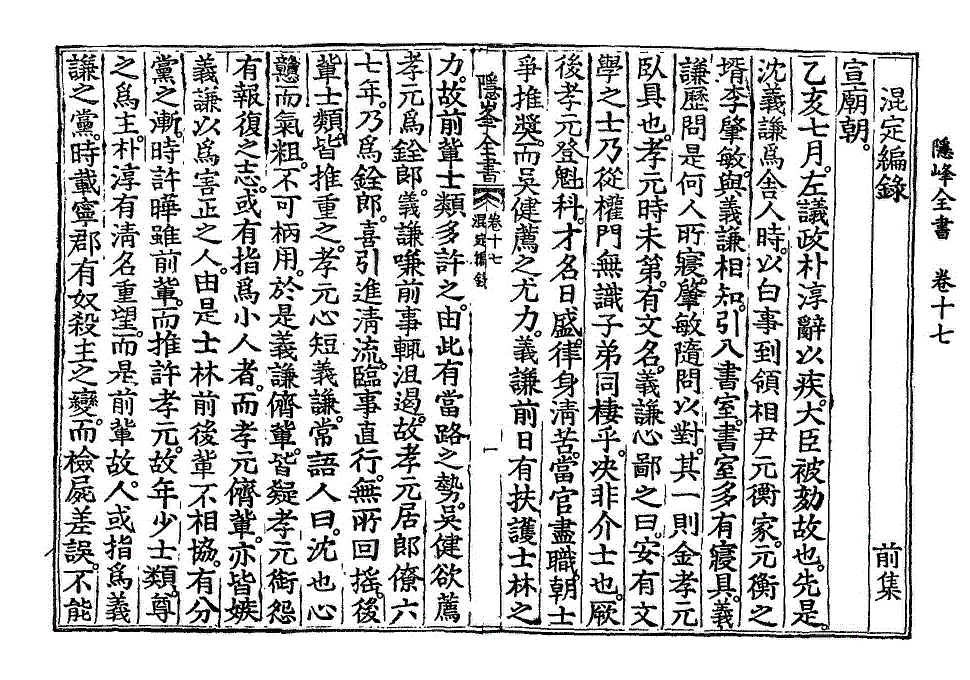 宣庙朝。
宣庙朝。乙亥七月。左议政朴淳辞以疾。大臣被劾故也。先是。沈义谦为舍人时。以白事到领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肇敏。与义谦相知。引入书室。书室多有寝具。义谦历问是何人所寝。肇敏随问以对。其一则金孝元卧具也。孝元时未第。有文名。义谦心鄙之曰。安有文学之士乃从权门无识子弟同栖乎。决非介士也。厥后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律身清苦。当官尽职。朝士争推奖。而吴健荐之尤力。义谦前日有扶护士林之力。故前辈士类多许之。由此有当路之势。吴健欲荐孝元为铨郎。义谦嗛前事辄沮遏。故孝元居郎僚六七年。乃为铨郎。喜引进清流。临事直行。无所回摇。后辈士类。皆推重之。孝元心短义谦。常语人曰。沈也心戆而气粗。不可柄用。于是义谦侪辈。皆疑孝元衔怨有报复之志。或有指为小人者。而孝元侪辈。亦皆嫉义谦以为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后辈不相协。有分党之渐。时许晔虽前辈。而推许孝元。故年少士类。尊之为主。朴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辈故。人或指为义谦之党。时载宁郡有奴杀主之变。而检尸差误。不能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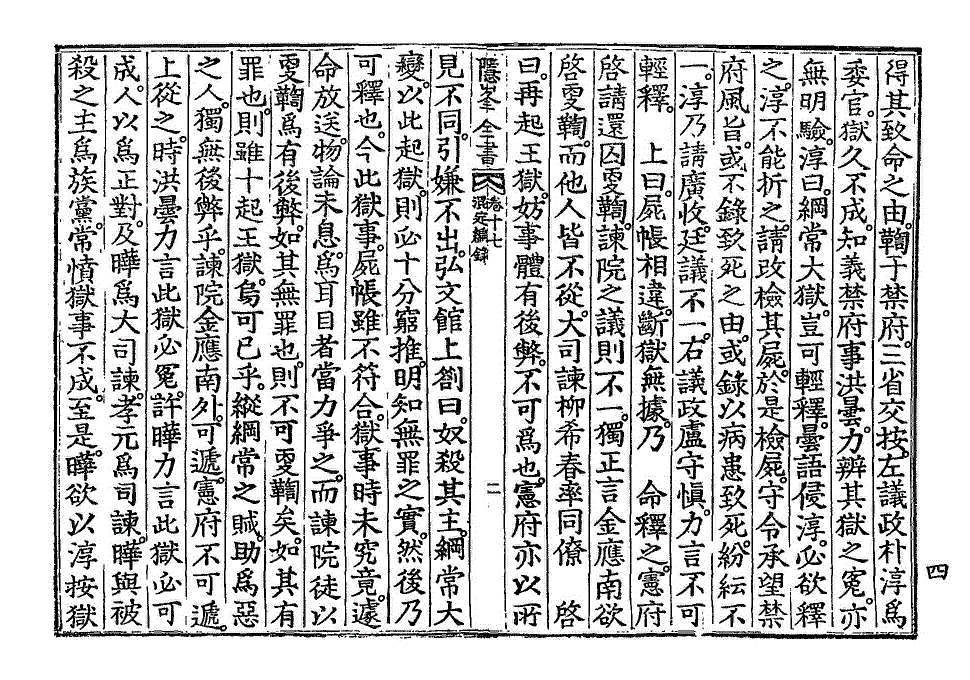 得其致命之由。鞫于禁府。三省交按。左议政朴淳为委官。狱久不成。知义禁府事洪昙。力辨其狱之冤。亦无明验。淳曰。纲常大狱。岂可轻释。昙语侵淳。必欲释之。淳不能折之。请改检其尸。于是检尸。守令承望禁府风旨。或不录致死之由。或录以病患致死。纷纭不一。淳乃请广收。廷议不一。右议政卢守慎。力言不可轻释。 上曰。尸帐相违。断狱无据。乃 命释之。宪府启请还囚更鞫。谏院之议则不一。独正言金应南欲启更鞫。而他人皆不从。大司谏柳希春率同僚 启曰。再起王狱。妨事体有后弊。不可为也。宪府亦以所见不同。引嫌不出。弘文馆上劄曰。奴杀其主。纲常大变。以此起狱。则必十分穷推。明知无罪之实。然后乃可释也。今此狱事。尸帐虽不符合。狱事时未究竟。遽命放送。物论未息。为耳目者当力争之。而谏院徒以更鞫为有后弊。如其无罪也。则不可更鞫矣。如其有罪也。则虽十起王狱。乌可已乎。纵纲常之贼。助为恶之人。独无后弊乎。谏院金应南外。可递。宪府不可递。上从之。时洪昙力言此狱必冤。许晔力言此狱必可成。人以为正对。及晔为大司谏。孝元为司谏。晔与被杀之主为族党。常愤狱事不成。至是。晔欲以淳按狱
得其致命之由。鞫于禁府。三省交按。左议政朴淳为委官。狱久不成。知义禁府事洪昙。力辨其狱之冤。亦无明验。淳曰。纲常大狱。岂可轻释。昙语侵淳。必欲释之。淳不能折之。请改检其尸。于是检尸。守令承望禁府风旨。或不录致死之由。或录以病患致死。纷纭不一。淳乃请广收。廷议不一。右议政卢守慎。力言不可轻释。 上曰。尸帐相违。断狱无据。乃 命释之。宪府启请还囚更鞫。谏院之议则不一。独正言金应南欲启更鞫。而他人皆不从。大司谏柳希春率同僚 启曰。再起王狱。妨事体有后弊。不可为也。宪府亦以所见不同。引嫌不出。弘文馆上劄曰。奴杀其主。纲常大变。以此起狱。则必十分穷推。明知无罪之实。然后乃可释也。今此狱事。尸帐虽不符合。狱事时未究竟。遽命放送。物论未息。为耳目者当力争之。而谏院徒以更鞫为有后弊。如其无罪也。则不可更鞫矣。如其有罪也。则虽十起王狱。乌可已乎。纵纲常之贼。助为恶之人。独无后弊乎。谏院金应南外。可递。宪府不可递。上从之。时洪昙力言此狱必冤。许晔力言此狱必可成。人以为正对。及晔为大司谏。孝元为司谏。晔与被杀之主为族党。常愤狱事不成。至是。晔欲以淳按狱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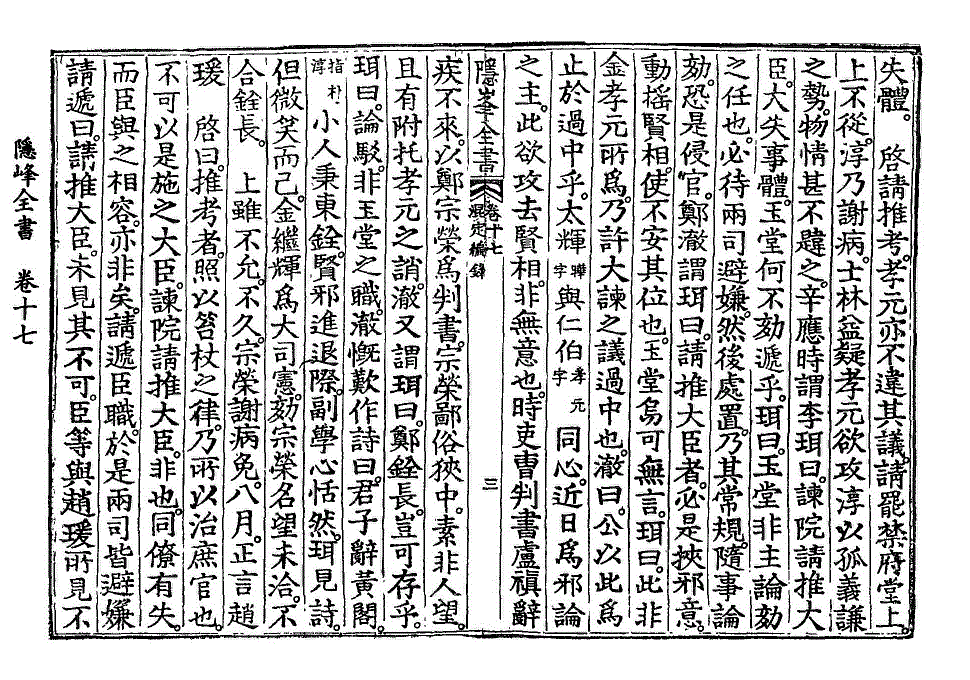 失体。 启请推考。孝元亦不违其议。请罢禁府堂上。上不从。淳乃谢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义谦之势。物情甚不韪之。辛应时谓李珥曰。谏院请推大臣。大失事体。玉堂何不劾递乎。珥曰。玉堂非主论劾之任也。必待两司避嫌。然后处置。乃其常规。随事论劾。恐是侵官。郑澈谓珥曰。请推大臣者。必是挟邪意。动摇贤相。使不安其位也。玉堂乌可无言。珥曰。此非金孝元所为。乃许大谏之议过中也。澈曰。公以此为止于过中乎。太辉(晔字)与仁伯(孝元字)同心。近日为邪论之主。此欲攻去贤相。非无意也。时吏曹判书卢禛辞疾不来。以郑宗荣为判书。宗荣鄙俗狭中。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诮。澈又谓珥曰。郑铨长。岂可存乎。珥曰。论驳。非玉堂之职。澈慨叹作诗曰。君子辞黄阁。(指朴淳)小人秉东铨。贤邪进退际。副学心恬然。珥见诗。但微笑而已。金继辉为大司宪。劾宗荣名望未洽。不合铨长。 上虽不允。不久。宗荣谢病免。八月。正言赵瑗 启曰。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乃所以治庶官也。不可以是施之大臣。谏院请推大臣。非也。同僚有失。而臣与之相容。亦非矣。请递臣职。于是两司皆避嫌请递曰。请推大臣。未见其不可。臣等与赵瑗所见不
失体。 启请推考。孝元亦不违其议。请罢禁府堂上。上不从。淳乃谢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义谦之势。物情甚不韪之。辛应时谓李珥曰。谏院请推大臣。大失事体。玉堂何不劾递乎。珥曰。玉堂非主论劾之任也。必待两司避嫌。然后处置。乃其常规。随事论劾。恐是侵官。郑澈谓珥曰。请推大臣者。必是挟邪意。动摇贤相。使不安其位也。玉堂乌可无言。珥曰。此非金孝元所为。乃许大谏之议过中也。澈曰。公以此为止于过中乎。太辉(晔字)与仁伯(孝元字)同心。近日为邪论之主。此欲攻去贤相。非无意也。时吏曹判书卢禛辞疾不来。以郑宗荣为判书。宗荣鄙俗狭中。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诮。澈又谓珥曰。郑铨长。岂可存乎。珥曰。论驳。非玉堂之职。澈慨叹作诗曰。君子辞黄阁。(指朴淳)小人秉东铨。贤邪进退际。副学心恬然。珥见诗。但微笑而已。金继辉为大司宪。劾宗荣名望未洽。不合铨长。 上虽不允。不久。宗荣谢病免。八月。正言赵瑗 启曰。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乃所以治庶官也。不可以是施之大臣。谏院请推大臣。非也。同僚有失。而臣与之相容。亦非矣。请递臣职。于是两司皆避嫌请递曰。请推大臣。未见其不可。臣等与赵瑗所见不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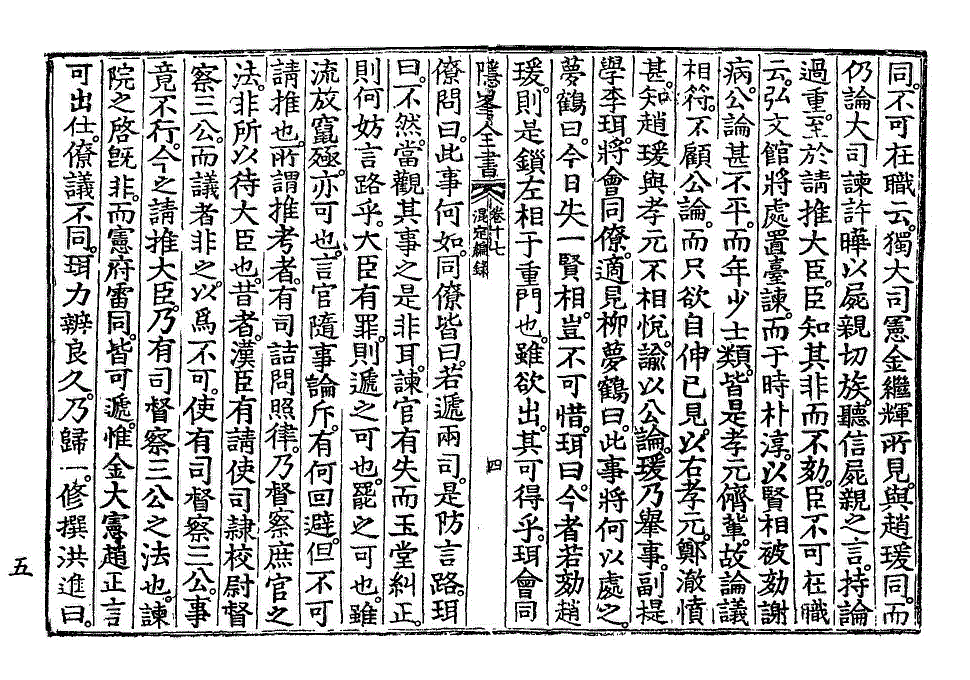 同。不可在职云。独大司宪金继辉所见。与赵瑗同。而仍论大司谏许晔以尸亲切族。听信尸亲之言。持论过重。至于请推大臣。臣知其非而不劾。臣不可在职云。弘文馆将处置台谏。而于时朴淳。以贤相被劾谢病。公论甚不平。而年少士类。皆是孝元侪辈。故论议相符。不顾公论。而只欲自伸己见。以右孝元。郑澈愤甚。知赵瑗与孝元不相悦。谕以公论。瑗乃举事。副提学李珥。将会同僚。适见柳梦鹤曰。此事将何以处之。梦鹤曰。今日失一贤相。岂不可惜。珥曰。今者若劾赵瑗。则是锁左相于重门也。虽欲出。其可得乎。珥会同僚问曰。此事何如。同僚皆曰。若递两司。是防言路。珥曰。不然。当观其事之是非耳。谏官有失而玉堂纠正。则何妨言路乎。大臣有罪。则递之可也。罢之可也。虽流放窜殛。亦可也。言官随事论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请推也。所谓推考者。有司诘问照律。乃督察庶官之法。非所以待大臣也。昔者。汉臣有请使司隶校尉督察三公。而议者非之。以为不可。使有司督察三公。事竟不行。今之请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之法也。谏院之启既非。而宪府雷同。皆可递。惟金大宪,赵正言可出仕。僚议不同。珥力辨良久。乃归一。修撰洪进曰。
同。不可在职云。独大司宪金继辉所见。与赵瑗同。而仍论大司谏许晔以尸亲切族。听信尸亲之言。持论过重。至于请推大臣。臣知其非而不劾。臣不可在职云。弘文馆将处置台谏。而于时朴淳。以贤相被劾谢病。公论甚不平。而年少士类。皆是孝元侪辈。故论议相符。不顾公论。而只欲自伸己见。以右孝元。郑澈愤甚。知赵瑗与孝元不相悦。谕以公论。瑗乃举事。副提学李珥。将会同僚。适见柳梦鹤曰。此事将何以处之。梦鹤曰。今日失一贤相。岂不可惜。珥曰。今者若劾赵瑗。则是锁左相于重门也。虽欲出。其可得乎。珥会同僚问曰。此事何如。同僚皆曰。若递两司。是防言路。珥曰。不然。当观其事之是非耳。谏官有失而玉堂纠正。则何妨言路乎。大臣有罪。则递之可也。罢之可也。虽流放窜殛。亦可也。言官随事论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请推也。所谓推考者。有司诘问照律。乃督察庶官之法。非所以待大臣也。昔者。汉臣有请使司隶校尉督察三公。而议者非之。以为不可。使有司督察三公。事竟不行。今之请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之法也。谏院之启既非。而宪府雷同。皆可递。惟金大宪,赵正言可出仕。僚议不同。珥力辨良久。乃归一。修撰洪进曰。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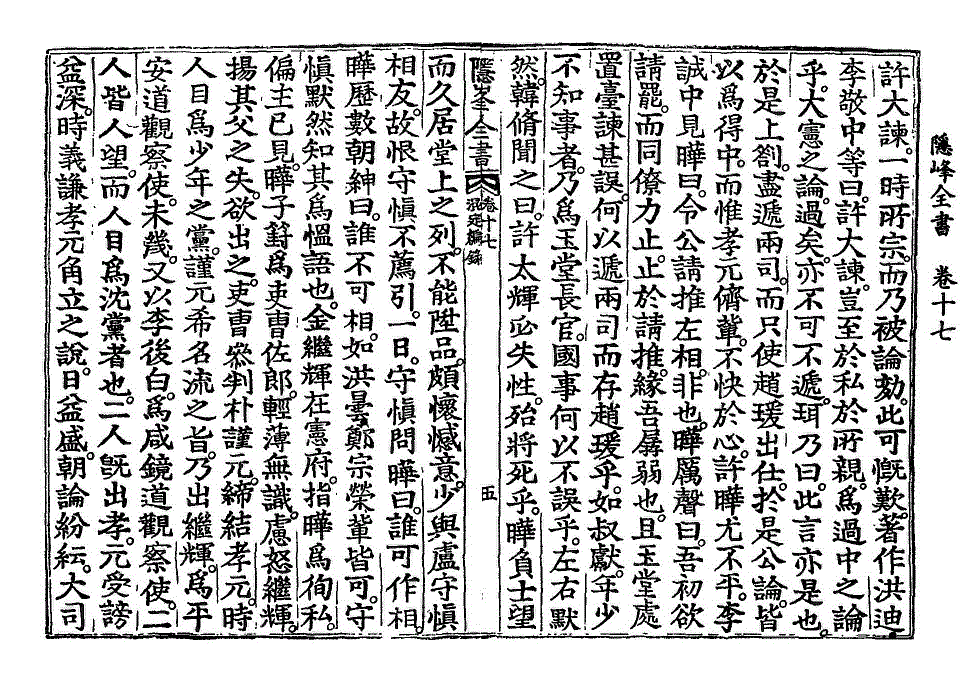 许大谏。一时所宗。而乃被论劾。此可慨叹。著作洪迪,李敬中等曰。许大谏。岂至于私于所亲。为过中之论乎。大宪之论。过矣。亦不可不递。珥乃曰。此言亦是也。于是上劄。尽递两司。而只使赵瑗出仕。于是公论。皆以为得中。而惟孝元侪辈。不快于心。许晔尤不平。李诚中见晔曰。令公请推左相。非也。晔厉声曰。吾初欲请罢。而同僚力止。止于请推。缘吾孱弱也。且玉堂处置台谏甚误。何以递两司而存赵瑗乎。如叔献。年少不知事者。乃为玉堂长官。国事何以不误乎。左右默然。韩脩闻之曰。许太辉必失性。殆将死乎。晔负士望而久居堂上之列。不能升品。颇怀憾意。少与卢守慎相友。故恨守慎不荐引。一日。守慎问晔曰。谁可作相。晔历数朝绅曰。谁不可相。如洪昙,郑宗荣辈皆可。守慎默然知其为愠语也。金继辉在宪府。指晔为徇私。偏主己见。晔子篈为吏曹佐郎。轻薄无识。虑怒继辉。扬其父之失。欲出之。吏曹参判朴谨元。缔结孝元。时人目为少年之党。谨元希名流之旨。乃出继辉。为平安道观察使。未几。又以李后白。为咸镜道观察使。二人皆人望。而人目为沈党者也。二人既出孝。元受谤益深。时义谦孝元角立之说。日益盛。朝论纷纭。大司
许大谏。一时所宗。而乃被论劾。此可慨叹。著作洪迪,李敬中等曰。许大谏。岂至于私于所亲。为过中之论乎。大宪之论。过矣。亦不可不递。珥乃曰。此言亦是也。于是上劄。尽递两司。而只使赵瑗出仕。于是公论。皆以为得中。而惟孝元侪辈。不快于心。许晔尤不平。李诚中见晔曰。令公请推左相。非也。晔厉声曰。吾初欲请罢。而同僚力止。止于请推。缘吾孱弱也。且玉堂处置台谏甚误。何以递两司而存赵瑗乎。如叔献。年少不知事者。乃为玉堂长官。国事何以不误乎。左右默然。韩脩闻之曰。许太辉必失性。殆将死乎。晔负士望而久居堂上之列。不能升品。颇怀憾意。少与卢守慎相友。故恨守慎不荐引。一日。守慎问晔曰。谁可作相。晔历数朝绅曰。谁不可相。如洪昙,郑宗荣辈皆可。守慎默然知其为愠语也。金继辉在宪府。指晔为徇私。偏主己见。晔子篈为吏曹佐郎。轻薄无识。虑怒继辉。扬其父之失。欲出之。吏曹参判朴谨元。缔结孝元。时人目为少年之党。谨元希名流之旨。乃出继辉。为平安道观察使。未几。又以李后白。为咸镜道观察使。二人皆人望。而人目为沈党者也。二人既出孝。元受谤益深。时义谦孝元角立之说。日益盛。朝论纷纭。大司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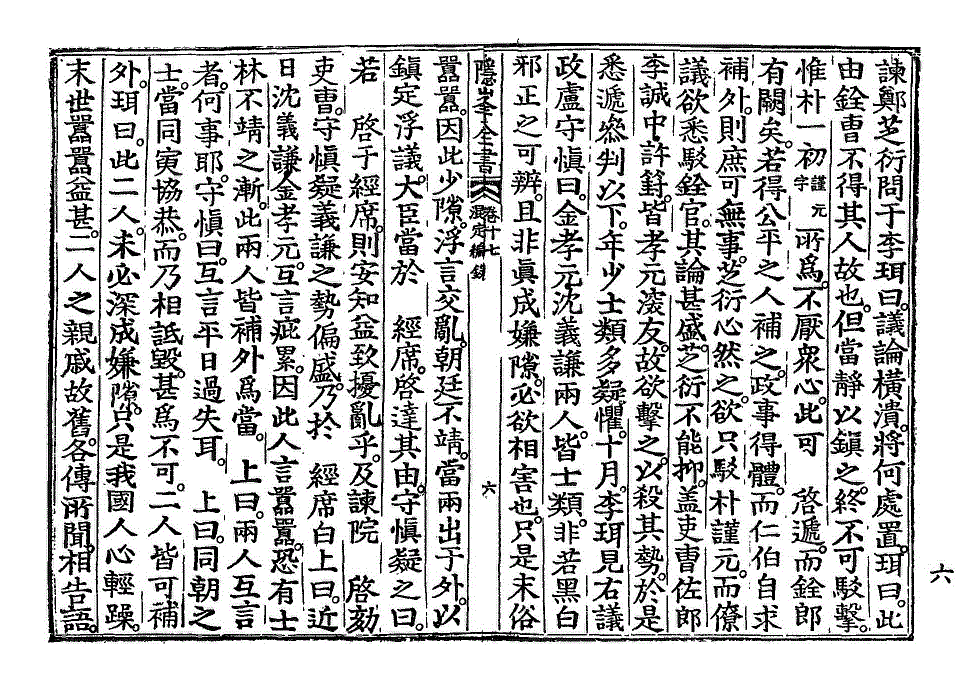 谏郑芝衍问于李珥曰。议论横溃。将何处置。珥曰。此由铨曹不得其人故也。但当静以镇之。终不可驳击。惟朴一初(谨元字)所为。不厌众心。此可 启递。而铨郎有阙矣。若得公平之人补之。政事得体。而仁伯自求补外。则庶可无事。芝衍心然之。欲只驳朴谨元。而僚议欲悉驳铨官。其论甚盛。芝衍不能抑。盖吏曹佐郎李诚中,许篈。皆孝元深友。故欲击之。以杀其势。于是悉递参判以下。年少士类多疑惧。十月。李珥见右议政卢守慎曰。金孝元,沈义谦两人。皆士类。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且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末俗嚣嚣。因此少隙。浮言交乱。朝廷不靖。当两出于外。以镇定浮议。大臣当于 经席。启达其由。守慎疑之曰。若 启于经席。则安知益致扰乱乎。及谏院 启劾吏曹。守慎疑义谦之势偏盛。乃于 经席白上曰。近日沈义谦,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嚣嚣。恐有士林不靖之渐。此两人皆补外为当。 上曰。两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慎曰。互言平日过失耳。 上曰。同朝之士。当同寅协恭。而乃相诋毁。甚为不可。二人皆可补外。珥曰。此二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国人心轻躁。末世嚣嚣益甚。二人之亲戚故旧。各传所闻。相告语。
谏郑芝衍问于李珥曰。议论横溃。将何处置。珥曰。此由铨曹不得其人故也。但当静以镇之。终不可驳击。惟朴一初(谨元字)所为。不厌众心。此可 启递。而铨郎有阙矣。若得公平之人补之。政事得体。而仁伯自求补外。则庶可无事。芝衍心然之。欲只驳朴谨元。而僚议欲悉驳铨官。其论甚盛。芝衍不能抑。盖吏曹佐郎李诚中,许篈。皆孝元深友。故欲击之。以杀其势。于是悉递参判以下。年少士类多疑惧。十月。李珥见右议政卢守慎曰。金孝元,沈义谦两人。皆士类。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且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末俗嚣嚣。因此少隙。浮言交乱。朝廷不靖。当两出于外。以镇定浮议。大臣当于 经席。启达其由。守慎疑之曰。若 启于经席。则安知益致扰乱乎。及谏院 启劾吏曹。守慎疑义谦之势偏盛。乃于 经席白上曰。近日沈义谦,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嚣嚣。恐有士林不靖之渐。此两人皆补外为当。 上曰。两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慎曰。互言平日过失耳。 上曰。同朝之士。当同寅协恭。而乃相诋毁。甚为不可。二人皆可补外。珥曰。此二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国人心轻躁。末世嚣嚣益甚。二人之亲戚故旧。各传所闻。相告语。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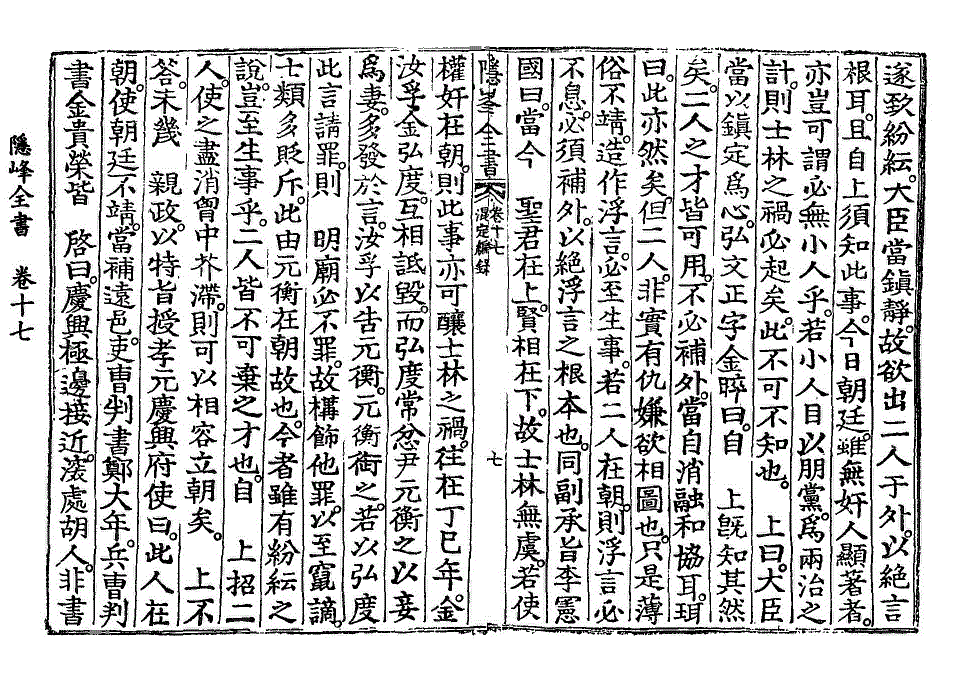 遂致纷纭。大臣当镇静。故欲出二人于外。以绝言根耳。且自上须知此事。今日朝廷。虽无奸人显著者。亦岂可谓必无小人乎。若小人目以朋党。为两治之计。则士林之祸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 上曰。大臣当以镇定为心。弘文正字金晬曰。自 上既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补外。当自消融和协耳。珥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实有仇嫌欲相图也。只是薄俗不靖。造作浮言。必至生事。若二人在朝。则浮言必不息。必须补外。以绝浮言之根本也。同副承旨李宪国曰。当今 圣君在上。贤相在下。故士林无虞。若使权奸在朝。则此事亦可酿士林之祸。往在丁巳年。金汝孚,金弘度。互相诋毁。而弘度常忿尹元衡之以妾为妻。多发于言。汝孚以告元衡。元衡衔之。若以弘度此言请罪。则 明庙必不罪。故构饰他罪。以至窜谪。士类多贬斥。此由元衡在朝故也。今者虽有纷纭之说。岂至生事乎。二人皆不可弃之才也。自 上招二人。使之尽消胸中芥滞。则可以相容立朝矣。 上不答。未几 亲政。以特旨授孝元庆兴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当补远邑。吏曹判书郑大年。兵曹判书金贵荣皆 启曰。庆兴极边接近。深处胡人。非书
遂致纷纭。大臣当镇静。故欲出二人于外。以绝言根耳。且自上须知此事。今日朝廷。虽无奸人显著者。亦岂可谓必无小人乎。若小人目以朋党。为两治之计。则士林之祸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 上曰。大臣当以镇定为心。弘文正字金晬曰。自 上既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补外。当自消融和协耳。珥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实有仇嫌欲相图也。只是薄俗不靖。造作浮言。必至生事。若二人在朝。则浮言必不息。必须补外。以绝浮言之根本也。同副承旨李宪国曰。当今 圣君在上。贤相在下。故士林无虞。若使权奸在朝。则此事亦可酿士林之祸。往在丁巳年。金汝孚,金弘度。互相诋毁。而弘度常忿尹元衡之以妾为妻。多发于言。汝孚以告元衡。元衡衔之。若以弘度此言请罪。则 明庙必不罪。故构饰他罪。以至窜谪。士类多贬斥。此由元衡在朝故也。今者虽有纷纭之说。岂至生事乎。二人皆不可弃之才也。自 上招二人。使之尽消胸中芥滞。则可以相容立朝矣。 上不答。未几 亲政。以特旨授孝元庆兴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当补远邑。吏曹判书郑大年。兵曹判书金贵荣皆 启曰。庆兴极边接近。深处胡人。非书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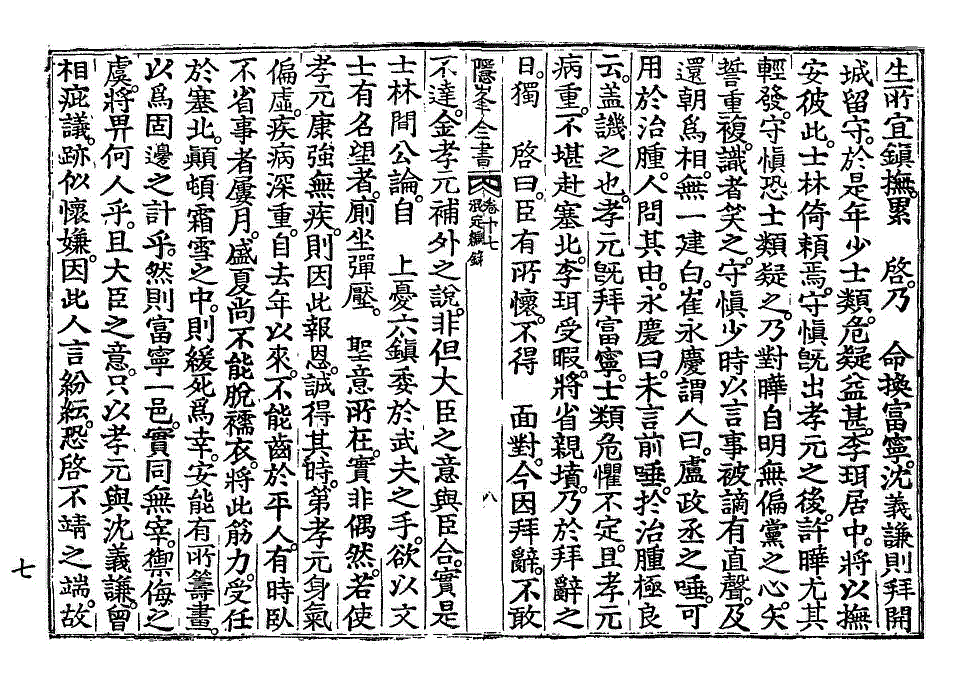 生所宜镇抚。累 启。乃 命换富宁。沈义谦则拜开城留守。于是年少士类。危疑益甚。李珥居中。将以抚安彼此。士林倚赖焉。守慎既出孝元之后。许晔尤其轻发。守慎恐士类疑之。乃对晔自明无偏党之心。矢誓重复。识者笑之。守慎少时以言事被谪有直声。及还朝为相。无一建白。崔永庆谓人曰。卢政丞之唾。可用于治肿。人问其由。永庆曰。未言前唾。于治肿极良云。盖讥之也。孝元既拜富宁。士类危惧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堪赴塞北。李珥受暇。将省亲坟。乃于拜辞之日。独 启曰。臣有所怀。不得 面对。今因拜辞。不敢不达。金孝元补外之说。非但大臣之意与臣合。实是士林间公论。自 上忧六镇委于武夫之手。欲以文士有名望者。厕坐弹压。 圣意所在。实非偶然。若使孝元康强无疾。则因此报恩。诚得其时。第孝元身气偏虚。疾病深重。自去年以来。不能齿于平人。有时卧不省事者屡月。盛夏尚不能脱襦衣。将此筋力。受任于塞北。颠顿霜雪之中。则缓死为幸。安能有所筹画。以为固边之计乎。然则富宁一邑。实同无宰。御侮之虞。将畀何人乎。且大臣之意。只以孝元与沈义谦。曾相疵议。迹似怀嫌。因此人言纷纭。恐启不靖之端。故
生所宜镇抚。累 启。乃 命换富宁。沈义谦则拜开城留守。于是年少士类。危疑益甚。李珥居中。将以抚安彼此。士林倚赖焉。守慎既出孝元之后。许晔尤其轻发。守慎恐士类疑之。乃对晔自明无偏党之心。矢誓重复。识者笑之。守慎少时以言事被谪有直声。及还朝为相。无一建白。崔永庆谓人曰。卢政丞之唾。可用于治肿。人问其由。永庆曰。未言前唾。于治肿极良云。盖讥之也。孝元既拜富宁。士类危惧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堪赴塞北。李珥受暇。将省亲坟。乃于拜辞之日。独 启曰。臣有所怀。不得 面对。今因拜辞。不敢不达。金孝元补外之说。非但大臣之意与臣合。实是士林间公论。自 上忧六镇委于武夫之手。欲以文士有名望者。厕坐弹压。 圣意所在。实非偶然。若使孝元康强无疾。则因此报恩。诚得其时。第孝元身气偏虚。疾病深重。自去年以来。不能齿于平人。有时卧不省事者屡月。盛夏尚不能脱襦衣。将此筋力。受任于塞北。颠顿霜雪之中。则缓死为幸。安能有所筹画。以为固边之计乎。然则富宁一邑。实同无宰。御侮之虞。将畀何人乎。且大臣之意。只以孝元与沈义谦。曾相疵议。迹似怀嫌。因此人言纷纭。恐启不靖之端。故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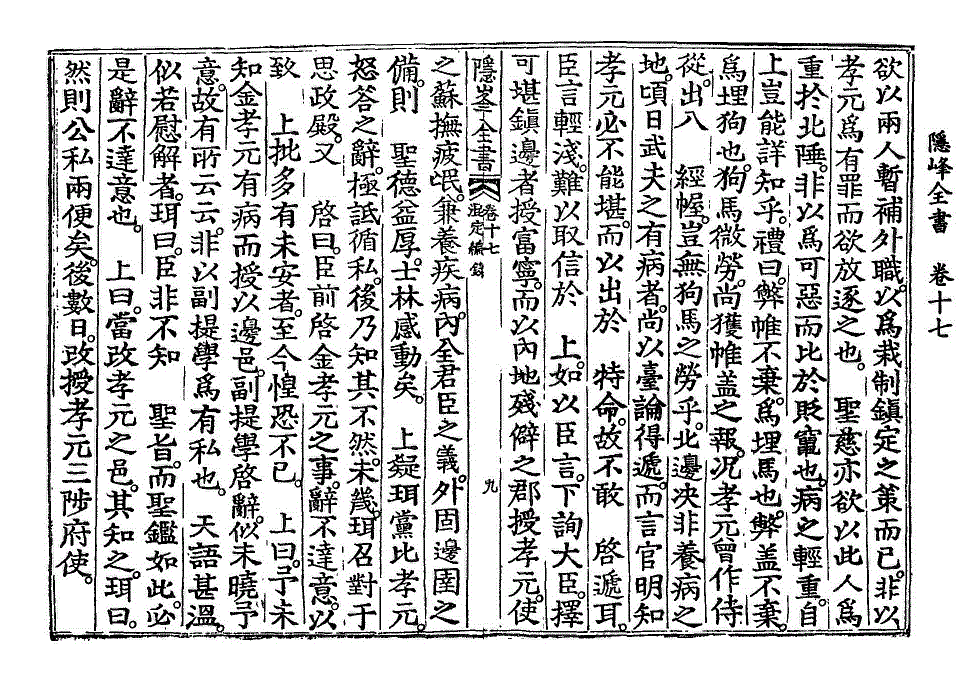 欲以两人暂补外职。以为栽制镇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为有罪而欲放逐之也。 圣慈亦欲以此人为重于北陲。非以为可恶而比于贬窜也。病之轻重。自上岂能详知乎。礼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狗马微劳。尚获帷盖之报。况孝元曾作侍从。出入 经幄。岂无狗马之劳乎。北边决非养病之地。顷日武夫之有病者。尚以台论得递。而言官明知孝元必不能堪。而以出于 特命。故不敢 启递耳。臣言轻浅。难以取信于 上。如以臣言。下询大臣。择可堪镇边者授富宁。而以内地残僻之郡授孝元。使之苏抚疲氓。兼养疾病。内全君臣之义。外固边圉之备。则 圣德益厚。士林感动矣。 上疑珥党比孝元。怒答之辞。极诋循私。后乃知其不然。未几。珥召对于思政殿。又 启曰。臣前启金孝元之事。辞不达意。以致 上批多有未安者。至今惶恐不已。 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以边邑。副提学启辞。似未晓予意。故有所云云。非以副提学为有私也。 天语甚温。似若慰解者。珥曰。臣非不知 圣旨。而圣鉴如此。必是辞不达意也。 上曰。当改孝元之邑。其知之。珥曰。然则公私两便矣。后数日。改授孝元三陟府使。
欲以两人暂补外职。以为栽制镇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为有罪而欲放逐之也。 圣慈亦欲以此人为重于北陲。非以为可恶而比于贬窜也。病之轻重。自上岂能详知乎。礼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狗马微劳。尚获帷盖之报。况孝元曾作侍从。出入 经幄。岂无狗马之劳乎。北边决非养病之地。顷日武夫之有病者。尚以台论得递。而言官明知孝元必不能堪。而以出于 特命。故不敢 启递耳。臣言轻浅。难以取信于 上。如以臣言。下询大臣。择可堪镇边者授富宁。而以内地残僻之郡授孝元。使之苏抚疲氓。兼养疾病。内全君臣之义。外固边圉之备。则 圣德益厚。士林感动矣。 上疑珥党比孝元。怒答之辞。极诋循私。后乃知其不然。未几。珥召对于思政殿。又 启曰。臣前启金孝元之事。辞不达意。以致 上批多有未安者。至今惶恐不已。 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以边邑。副提学启辞。似未晓予意。故有所云云。非以副提学为有私也。 天语甚温。似若慰解者。珥曰。臣非不知 圣旨。而圣鉴如此。必是辞不达意也。 上曰。当改孝元之邑。其知之。珥曰。然则公私两便矣。后数日。改授孝元三陟府使。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8L 页
 丙子二月。李珥弃官归乡。珥既递副提学。朴淳每于经席。荐其贤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矫激。且渠不欲事予。予何为强留乎。自古许退而俾遂其志者亦多矣。且贾谊。读书能言而已。实非可用之才。汉文之不用。真有所见也。副提学尹根寿见珥曰。自 上方以君之欲退为矫激。不欲留之云。君不可迟留乎。珥曰。自 上不欲留。则虽欲迟留。其可得乎。固将退也。闻许其退而乃不退。则是以去就为市道也。先是。金孝元喜荐引名流。年少士类。归重焉。势焰甚盛。前辈士类恶之。而畏其势莫敢下手。李珥在朝。恐其骎骎为朝廷不和之渐。欲杀其势。乃唱补外之说。公论倚之为重。珥意只欲镇定而已。非欲深治也。既出孝元。朝论便激。欲深治之。珥极力止之。且引李泼。复为铨郎。时辈欲以尹晛荐铨郎。珥心知晛不合于铨曹而为调剂。故不敢止。且以为李泼在铨。必能制晛之行私。及晛为吏郎。泼适以都承旨。知吏曹朴好元同婿。有相避之规。故事。只以都承旨。改知他曹。而吏郎则不递。政院请改好元知他曹。 上曰。李泼非不可递之人也。乃递泼。晛始得用事。欲荐赵瑗为吏郎。瑗轻躁非人才。只是与孝元相失。而为正言时。唱递两司。以杀孝
丙子二月。李珥弃官归乡。珥既递副提学。朴淳每于经席。荐其贤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矫激。且渠不欲事予。予何为强留乎。自古许退而俾遂其志者亦多矣。且贾谊。读书能言而已。实非可用之才。汉文之不用。真有所见也。副提学尹根寿见珥曰。自 上方以君之欲退为矫激。不欲留之云。君不可迟留乎。珥曰。自 上不欲留。则虽欲迟留。其可得乎。固将退也。闻许其退而乃不退。则是以去就为市道也。先是。金孝元喜荐引名流。年少士类。归重焉。势焰甚盛。前辈士类恶之。而畏其势莫敢下手。李珥在朝。恐其骎骎为朝廷不和之渐。欲杀其势。乃唱补外之说。公论倚之为重。珥意只欲镇定而已。非欲深治也。既出孝元。朝论便激。欲深治之。珥极力止之。且引李泼。复为铨郎。时辈欲以尹晛荐铨郎。珥心知晛不合于铨曹而为调剂。故不敢止。且以为李泼在铨。必能制晛之行私。及晛为吏郎。泼适以都承旨。知吏曹朴好元同婿。有相避之规。故事。只以都承旨。改知他曹。而吏郎则不递。政院请改好元知他曹。 上曰。李泼非不可递之人也。乃递泼。晛始得用事。欲荐赵瑗为吏郎。瑗轻躁非人才。只是与孝元相失。而为正言时。唱递两司。以杀孝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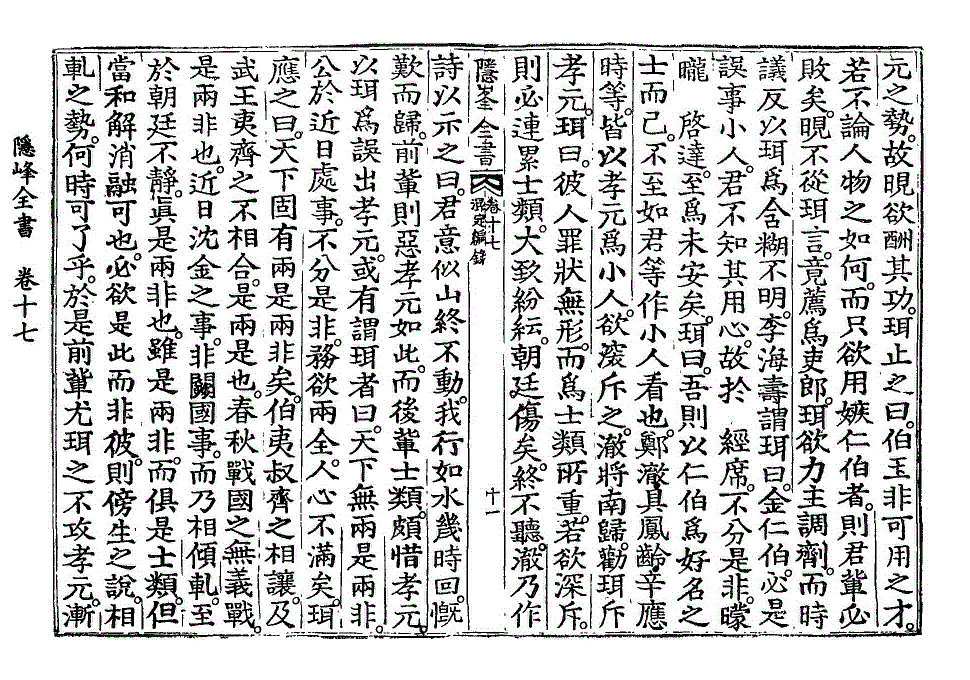 元之势。故晛欲酬其功。珥止之曰。伯玉非可用之才。若不论人物之如何。而只欲用嫉仁伯者。则君辈必败矣。晛不从珥言。竟荐为吏郎。珥欲力主调剂。而时议反以珥为含糊不明。李海寿谓珥曰。金仁伯。必是误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于 经席。不分是非。曚昽 启达。至为未安矣。珥曰。吾则以仁伯为好名之士而已。不至如君等作小人看也。郑澈,具凤龄,辛应时等。皆以孝元为小人。欲深斥之。澈将南归。劝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状无形。而为士类所重。若欲深斥。则必连累士类。大致纷纭。朝廷伤矣。终不听。澈乃作诗以示之曰。君意似山终不动。我行如水几时回。慨叹而归。前辈则恶孝元如此。而后辈士类。颇惜孝元。以珥为误出孝元。或有谓珥者曰。天下无两是两非。公于近日处事。不分是非。务欲两全。人心不满矣。珥应之曰。天下固有两是两非矣。伯夷叔齐之相让。及武王夷齐之不相合。是两是也。春秋战国之无义战。是两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关国事。而乃相倾轧。至于朝廷不静。真是两非也。虽是两非。而俱是士类。但当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则傍生之说。相轧之势。何时可了乎。于是前辈尤珥之不攻孝元。渐
元之势。故晛欲酬其功。珥止之曰。伯玉非可用之才。若不论人物之如何。而只欲用嫉仁伯者。则君辈必败矣。晛不从珥言。竟荐为吏郎。珥欲力主调剂。而时议反以珥为含糊不明。李海寿谓珥曰。金仁伯。必是误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于 经席。不分是非。曚昽 启达。至为未安矣。珥曰。吾则以仁伯为好名之士而已。不至如君等作小人看也。郑澈,具凤龄,辛应时等。皆以孝元为小人。欲深斥之。澈将南归。劝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状无形。而为士类所重。若欲深斥。则必连累士类。大致纷纭。朝廷伤矣。终不听。澈乃作诗以示之曰。君意似山终不动。我行如水几时回。慨叹而归。前辈则恶孝元如此。而后辈士类。颇惜孝元。以珥为误出孝元。或有谓珥者曰。天下无两是两非。公于近日处事。不分是非。务欲两全。人心不满矣。珥应之曰。天下固有两是两非矣。伯夷叔齐之相让。及武王夷齐之不相合。是两是也。春秋战国之无义战。是两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关国事。而乃相倾轧。至于朝廷不静。真是两非也。虽是两非。而俱是士类。但当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则傍生之说。相轧之势。何时可了乎。于是前辈尤珥之不攻孝元。渐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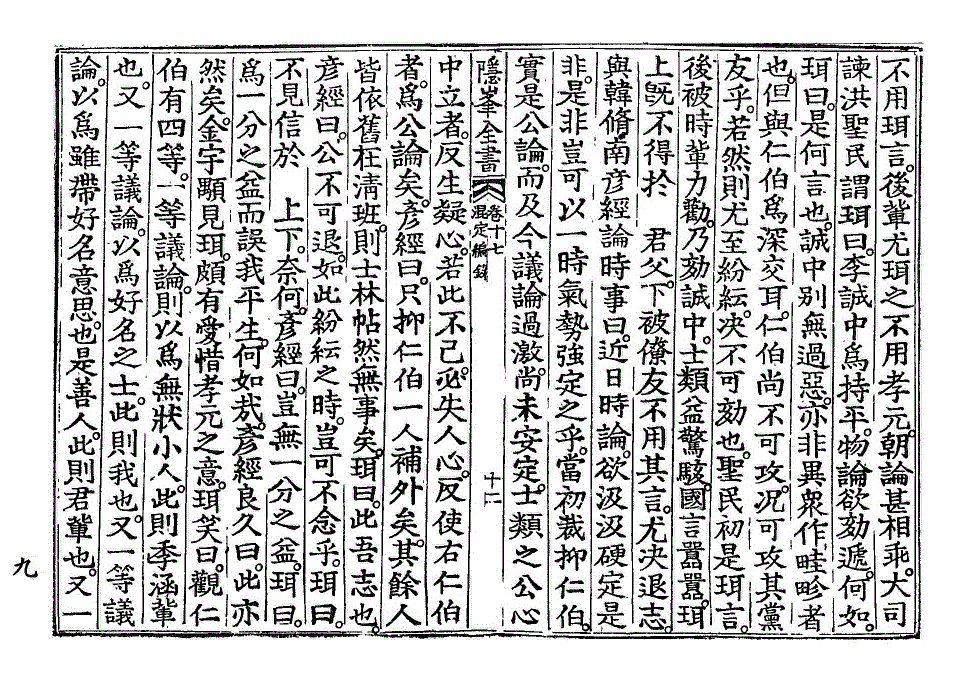 不用珥言。后辈尤珥之不用孝元。朝论甚相乖。大司谏洪圣民谓珥曰。李诚中为持平。物论欲劾递。何如。珥曰。是何言也。诚中别无过恶。亦非异众作畦畛者也。但与仁伯为深交耳。仁伯尚不可攻。况可攻其党友乎。若然则尤至纷纭。决不可劾也。圣民初是珥言。后被时辈力劝。乃劾诚中。士类益惊骇。国言嚣嚣。珥上既不得于 君父。下被僚友不用其言。尤决退志。与韩脩,南彦经论时事曰。近日时论。欲汲汲硬定是非。是非岂可以一时气势强定之乎。当初裁抑仁伯。实是公论。而及今议论过激。尚未安定。士类之公心中立者。反生疑心。若此不已。必失人心。反使右仁伯者。为公论矣。彦经曰。只抑仁伯一人补外矣。其馀人皆依旧在清班。则士林帖然无事矣。珥曰。此吾志也。彦经曰。公不可退。如此纷纭之时。岂可不念乎。珥曰。不见信于 上下。奈何。彦经曰。岂无一分之益。珥曰。为一分之益而误我平生。何如哉。彦经良久曰。此亦然矣。金宇颙见珥。颇有爱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观仁伯有四等。一等议论。则以为无状小人。此则季涵辈也。又一等议论。以为好名之士。此则我也。又一等议论。以为虽带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则君辈也。又一
不用珥言。后辈尤珥之不用孝元。朝论甚相乖。大司谏洪圣民谓珥曰。李诚中为持平。物论欲劾递。何如。珥曰。是何言也。诚中别无过恶。亦非异众作畦畛者也。但与仁伯为深交耳。仁伯尚不可攻。况可攻其党友乎。若然则尤至纷纭。决不可劾也。圣民初是珥言。后被时辈力劝。乃劾诚中。士类益惊骇。国言嚣嚣。珥上既不得于 君父。下被僚友不用其言。尤决退志。与韩脩,南彦经论时事曰。近日时论。欲汲汲硬定是非。是非岂可以一时气势强定之乎。当初裁抑仁伯。实是公论。而及今议论过激。尚未安定。士类之公心中立者。反生疑心。若此不已。必失人心。反使右仁伯者。为公论矣。彦经曰。只抑仁伯一人补外矣。其馀人皆依旧在清班。则士林帖然无事矣。珥曰。此吾志也。彦经曰。公不可退。如此纷纭之时。岂可不念乎。珥曰。不见信于 上下。奈何。彦经曰。岂无一分之益。珥曰。为一分之益而误我平生。何如哉。彦经良久曰。此亦然矣。金宇颙见珥。颇有爱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观仁伯有四等。一等议论。则以为无状小人。此则季涵辈也。又一等议论。以为好名之士。此则我也。又一等议论。以为虽带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则君辈也。又一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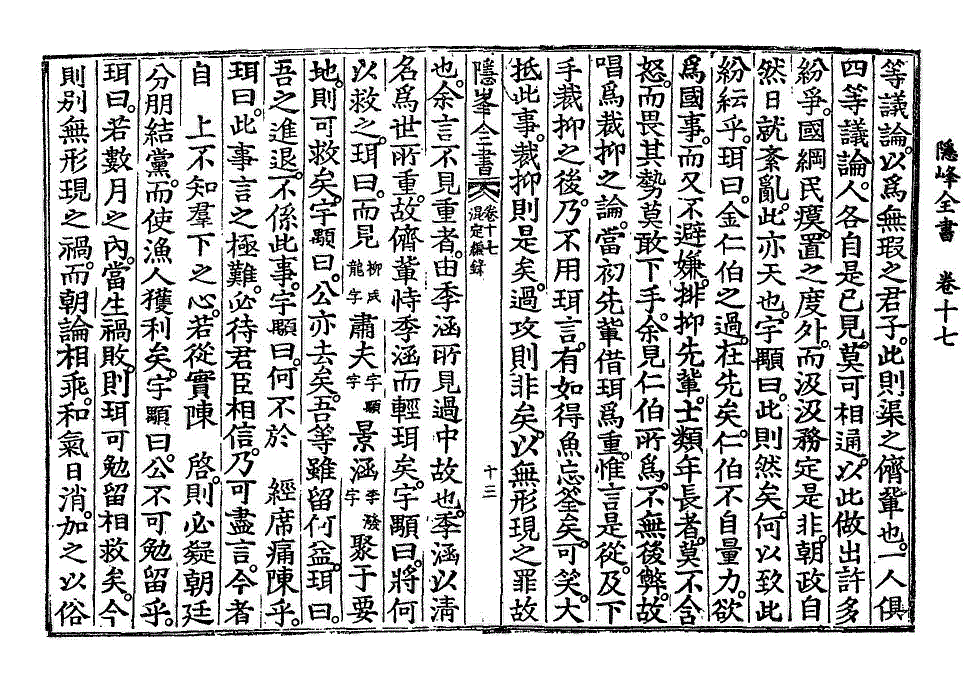 等议论。以为无瑕之君子。此则渠之侪辈也。一人俱四等议论。人各自是己见。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许多纷争。国纲民瘼。置之度外。而汲汲务定是非。朝政自然日就紊乱。此亦天也。宇颙曰。此则然矣。何以致此纷纭乎。珥曰。金仁伯之过。在先矣。仁伯不自量力。欲为国事。而又不避嫌。排抑先辈。士类年长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势莫敢下手。余见仁伯所为。不无后弊。故唱为裁抑之论。当初先辈借珥为重。惟言是从。及下手裁抑之后。乃不用珥言。有如得鱼忘筌矣。可笑。大抵此事。裁抑则是矣。过攻则非矣。以无形现之罪故也。余言不见重者。由季涵所见过中故也。季涵以清名为世所重。故侪辈恃季涵而轻珥矣。宇颙曰。将何以救之。珥曰。而见(柳成龙字)肃夫(宇颙字)景涵(李泼字)聚于要地。则可救矣。宇颙曰。公亦去矣。吾等虽留何益。珥曰。吾之进退。不系此事。宇颙曰。何不于 经席痛陈乎。珥曰。此事言之极难。必待君臣相信。乃可尽言。今者自 上不知群下之心。若从实陈 启。则必疑朝廷分朋结党。而使渔人获利矣。宇颙曰。公不可勉留乎。珥曰。若数月之内。当生祸败。则珥可勉留相救矣。今则别无形现之祸。而朝论相乖。和气日消。加之以俗
等议论。以为无瑕之君子。此则渠之侪辈也。一人俱四等议论。人各自是己见。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许多纷争。国纲民瘼。置之度外。而汲汲务定是非。朝政自然日就紊乱。此亦天也。宇颙曰。此则然矣。何以致此纷纭乎。珥曰。金仁伯之过。在先矣。仁伯不自量力。欲为国事。而又不避嫌。排抑先辈。士类年长者。莫不含怒。而畏其势莫敢下手。余见仁伯所为。不无后弊。故唱为裁抑之论。当初先辈借珥为重。惟言是从。及下手裁抑之后。乃不用珥言。有如得鱼忘筌矣。可笑。大抵此事。裁抑则是矣。过攻则非矣。以无形现之罪故也。余言不见重者。由季涵所见过中故也。季涵以清名为世所重。故侪辈恃季涵而轻珥矣。宇颙曰。将何以救之。珥曰。而见(柳成龙字)肃夫(宇颙字)景涵(李泼字)聚于要地。则可救矣。宇颙曰。公亦去矣。吾等虽留何益。珥曰。吾之进退。不系此事。宇颙曰。何不于 经席痛陈乎。珥曰。此事言之极难。必待君臣相信。乃可尽言。今者自 上不知群下之心。若从实陈 启。则必疑朝廷分朋结党。而使渔人获利矣。宇颙曰。公不可勉留乎。珥曰。若数月之内。当生祸败。则珥可勉留相救矣。今则别无形现之祸。而朝论相乖。和气日消。加之以俗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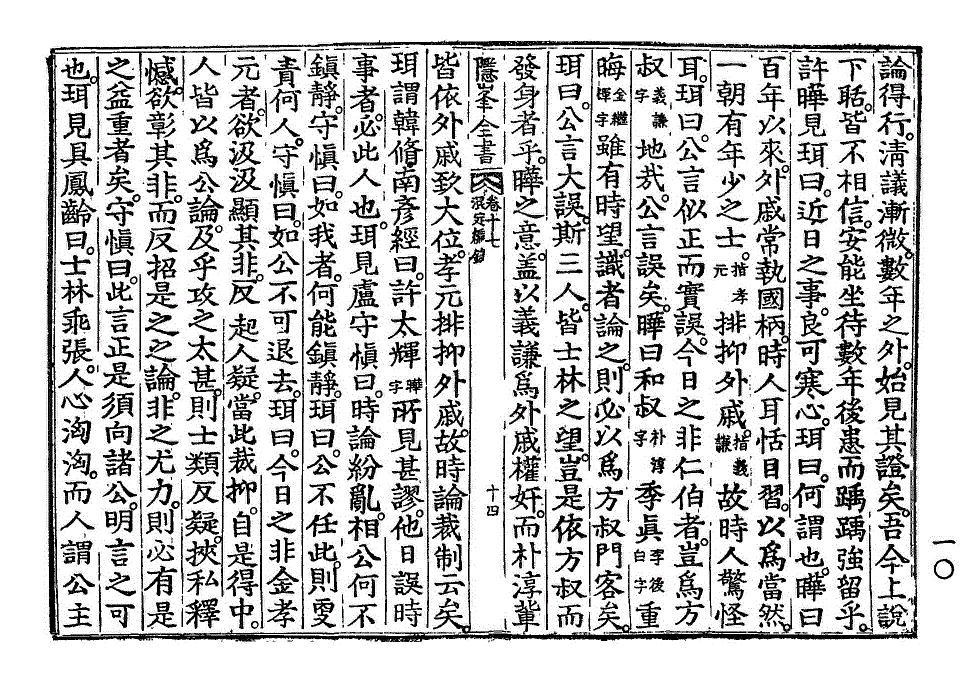 论得行。清议渐微。数年之外。始见其證矣。吾今上说下聒。皆不相信。安能坐待数年后患而踽踽强留乎。许晔见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谓也。晔曰百年以来。外戚常执国柄。时人耳恬目习。以为当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指孝元)排抑外戚。(指义谦)故时人惊怪耳。珥曰。公言似正而实误。今日之非仁伯者。岂为方叔(义谦字)地哉。公言误矣。晔曰和叔(朴淳字)季真(李后白字)重晦(金继辉字)虽有时望。识者论之。则必以为方叔门客矣。珥曰。公言大误。斯三人。皆士林之望。岂是依方叔而发身者乎。晔之意。盖以义谦为外戚权奸。而朴淳辈皆依外戚致大位。孝元排抑外戚。故时论裁制云矣。珥谓韩脩,南彦经曰。许太辉(晔字)所见甚谬。他日误时事者。必此人也。珥见卢守慎曰。时论纷乱。相公何不镇静。守慎曰。如我者。何能镇静。珥曰。公不任此。则更责何人。守慎曰。如公不可退去。珥曰。今日之非金孝元者。欲汲汲显其非。反起人疑。当此裁抑。自是得中。人皆以为公论。及乎攻之太甚。则士类反疑。挟私释憾。欲彰其非。而反招是之之论。非之尤力。则必有是之益重者矣。守慎曰。此言正是须向诸公。明言之可也。珥见具凤龄曰。士林乖张。人心汹汹。而人谓公主
论得行。清议渐微。数年之外。始见其證矣。吾今上说下聒。皆不相信。安能坐待数年后患而踽踽强留乎。许晔见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谓也。晔曰百年以来。外戚常执国柄。时人耳恬目习。以为当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指孝元)排抑外戚。(指义谦)故时人惊怪耳。珥曰。公言似正而实误。今日之非仁伯者。岂为方叔(义谦字)地哉。公言误矣。晔曰和叔(朴淳字)季真(李后白字)重晦(金继辉字)虽有时望。识者论之。则必以为方叔门客矣。珥曰。公言大误。斯三人。皆士林之望。岂是依方叔而发身者乎。晔之意。盖以义谦为外戚权奸。而朴淳辈皆依外戚致大位。孝元排抑外戚。故时论裁制云矣。珥谓韩脩,南彦经曰。许太辉(晔字)所见甚谬。他日误时事者。必此人也。珥见卢守慎曰。时论纷乱。相公何不镇静。守慎曰。如我者。何能镇静。珥曰。公不任此。则更责何人。守慎曰。如公不可退去。珥曰。今日之非金孝元者。欲汲汲显其非。反起人疑。当此裁抑。自是得中。人皆以为公论。及乎攻之太甚。则士类反疑。挟私释憾。欲彰其非。而反招是之之论。非之尤力。则必有是之益重者矣。守慎曰。此言正是须向诸公。明言之可也。珥见具凤龄曰。士林乖张。人心汹汹。而人谓公主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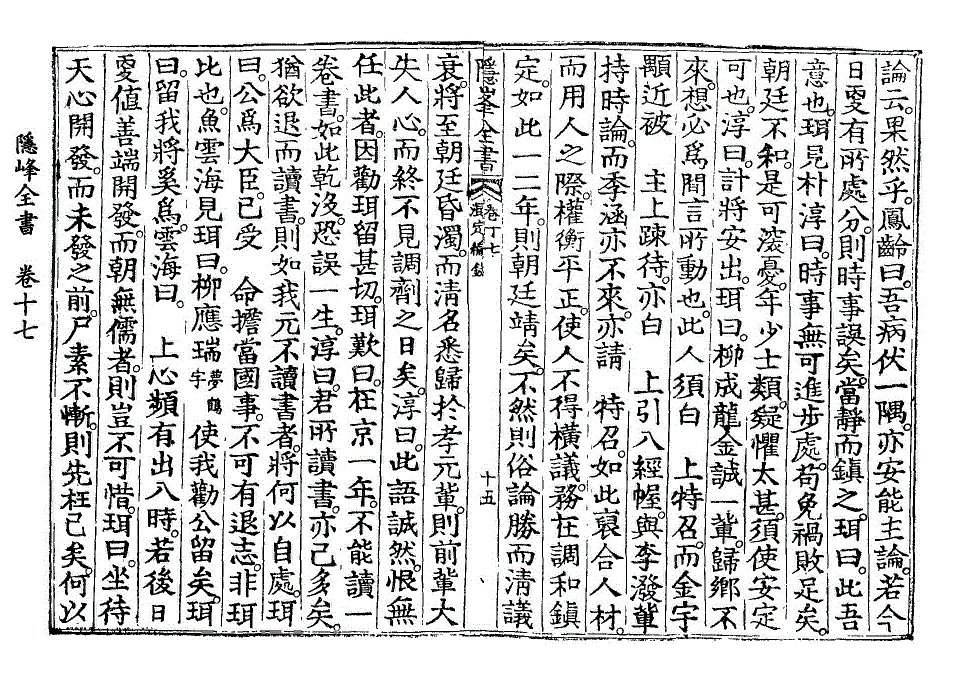 论云。果然乎。凤龄曰。吾病伏一隅。亦安能主论。若今日更有所处分。则时事误矣。当静而镇之。珥曰。此吾意也。珥见朴淳曰。时事无可进步处。苟免祸败足矣。朝廷不和。是可深忧。年少士类。疑惧太甚。须使安定可也。淳曰。计将安出。珥曰。柳成龙,金诚一辈。归乡不来。想必为间言所动也。此人须白 上特召。而金宇颙近被 主上疏待。亦白 上引入经幄。与李泼辈持时论。而季涵亦不来。亦请 特召。如此裒合人材。而用人之际。权衡平正。使人不得横议。务在调和镇定。如此一二年。则朝廷靖矣。不然则俗论胜而清议衰。将至朝廷昏浊。而清名悉归于孝元辈。则前辈大失人心。而终不见调剂之日矣。淳曰。此语诚然。恨无任此者。因劝珥留甚切。珥叹曰。在京一年。不能读一卷书。如此乾没。恐误一生。淳曰。君所读书。亦已多矣。犹欲退而读书。则如我元不读书者。将何以自处。珥曰。公为大臣。已受 命担当国事。不可有退志。非珥比也。鱼云海见珥曰。柳应瑞(梦鹤字)使我劝公留矣。珥曰。留我将奚为。云海曰。 上心频有出入时。若后日更值善端开发。而朝无儒者。则岂不可惜。珥曰。坐待天心开发。而未发之前。尸素不惭。则先枉己矣。何以
论云。果然乎。凤龄曰。吾病伏一隅。亦安能主论。若今日更有所处分。则时事误矣。当静而镇之。珥曰。此吾意也。珥见朴淳曰。时事无可进步处。苟免祸败足矣。朝廷不和。是可深忧。年少士类。疑惧太甚。须使安定可也。淳曰。计将安出。珥曰。柳成龙,金诚一辈。归乡不来。想必为间言所动也。此人须白 上特召。而金宇颙近被 主上疏待。亦白 上引入经幄。与李泼辈持时论。而季涵亦不来。亦请 特召。如此裒合人材。而用人之际。权衡平正。使人不得横议。务在调和镇定。如此一二年。则朝廷靖矣。不然则俗论胜而清议衰。将至朝廷昏浊。而清名悉归于孝元辈。则前辈大失人心。而终不见调剂之日矣。淳曰。此语诚然。恨无任此者。因劝珥留甚切。珥叹曰。在京一年。不能读一卷书。如此乾没。恐误一生。淳曰。君所读书。亦已多矣。犹欲退而读书。则如我元不读书者。将何以自处。珥曰。公为大臣。已受 命担当国事。不可有退志。非珥比也。鱼云海见珥曰。柳应瑞(梦鹤字)使我劝公留矣。珥曰。留我将奚为。云海曰。 上心频有出入时。若后日更值善端开发。而朝无儒者。则岂不可惜。珥曰。坐待天心开发。而未发之前。尸素不惭。则先枉己矣。何以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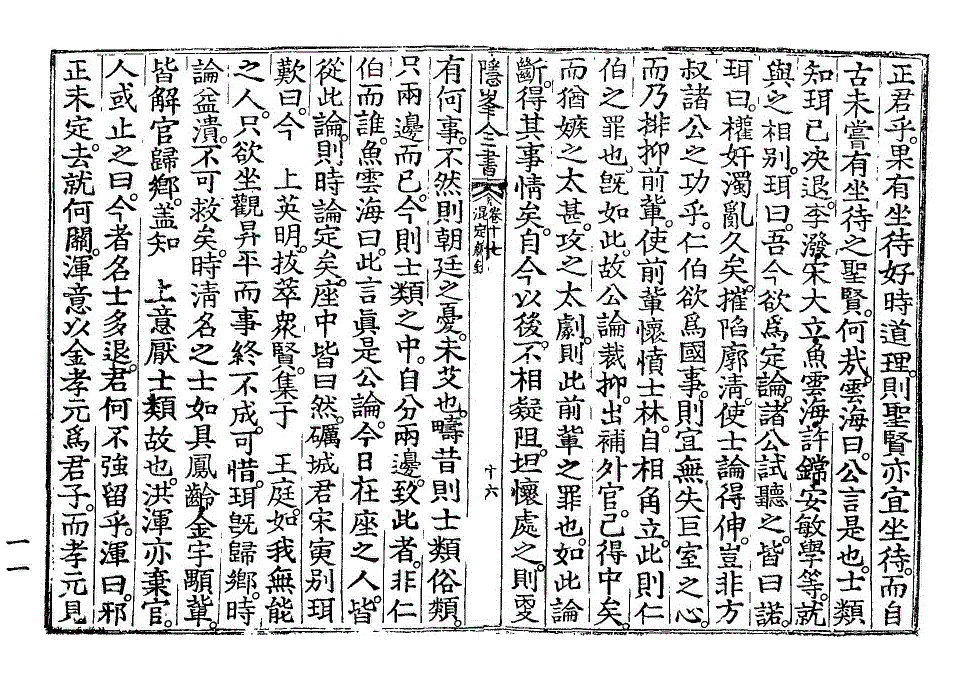 正君乎。果有坐待好时道理。则圣贤亦宜坐待。而自古未尝有坐待之圣贤。何哉。云海曰。公言是也。士类知珥已决退。李泼,宋大立,鱼云海,许鋿,安敏学等。就与之相别。珥曰。吾今欲为定论。诸公试听之。皆曰诺。珥曰。权奸浊乱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论得伸。岂非方叔诸公之功乎。仁伯欲为国事。则宜无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辈。使前辈怀愤士林。自相角立。此则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论裁抑。出补外官。已得中矣。而犹嫉之太甚。攻之太剧。则此前辈之罪也。如此论断。得其事情矣。自今以后。不相疑阻。坦怀处之。则更有何事。不然则朝廷之忧。未艾也。畴昔则士类俗类。只两边而已。今则士类之中。自分两边。致此者。非仁伯而谁。鱼云海曰。此言真是公论。今日在座之人。皆从此论。则时论定矣。座中皆曰然。砺城君宋寅别珥叹曰。今 上英明。拔萃众贤。集于 王庭。如我无能之人。只欲坐观升平而事终不成。可惜。珥既归乡。时论益溃。不可救矣。时清名之士如具凤龄,金宇颙辈。皆解官归乡。盖知 上意厌士类故也。洪浑亦弃官。人或止之曰。今者名士多退。君何不强留乎。浑曰。邪正未定。去就何关。浑意以金孝元为君子。而孝元见
正君乎。果有坐待好时道理。则圣贤亦宜坐待。而自古未尝有坐待之圣贤。何哉。云海曰。公言是也。士类知珥已决退。李泼,宋大立,鱼云海,许鋿,安敏学等。就与之相别。珥曰。吾今欲为定论。诸公试听之。皆曰诺。珥曰。权奸浊乱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论得伸。岂非方叔诸公之功乎。仁伯欲为国事。则宜无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辈。使前辈怀愤士林。自相角立。此则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论裁抑。出补外官。已得中矣。而犹嫉之太甚。攻之太剧。则此前辈之罪也。如此论断。得其事情矣。自今以后。不相疑阻。坦怀处之。则更有何事。不然则朝廷之忧。未艾也。畴昔则士类俗类。只两边而已。今则士类之中。自分两边。致此者。非仁伯而谁。鱼云海曰。此言真是公论。今日在座之人。皆从此论。则时论定矣。座中皆曰然。砺城君宋寅别珥叹曰。今 上英明。拔萃众贤。集于 王庭。如我无能之人。只欲坐观升平而事终不成。可惜。珥既归乡。时论益溃。不可救矣。时清名之士如具凤龄,金宇颙辈。皆解官归乡。盖知 上意厌士类故也。洪浑亦弃官。人或止之曰。今者名士多退。君何不强留乎。浑曰。邪正未定。去就何关。浑意以金孝元为君子。而孝元见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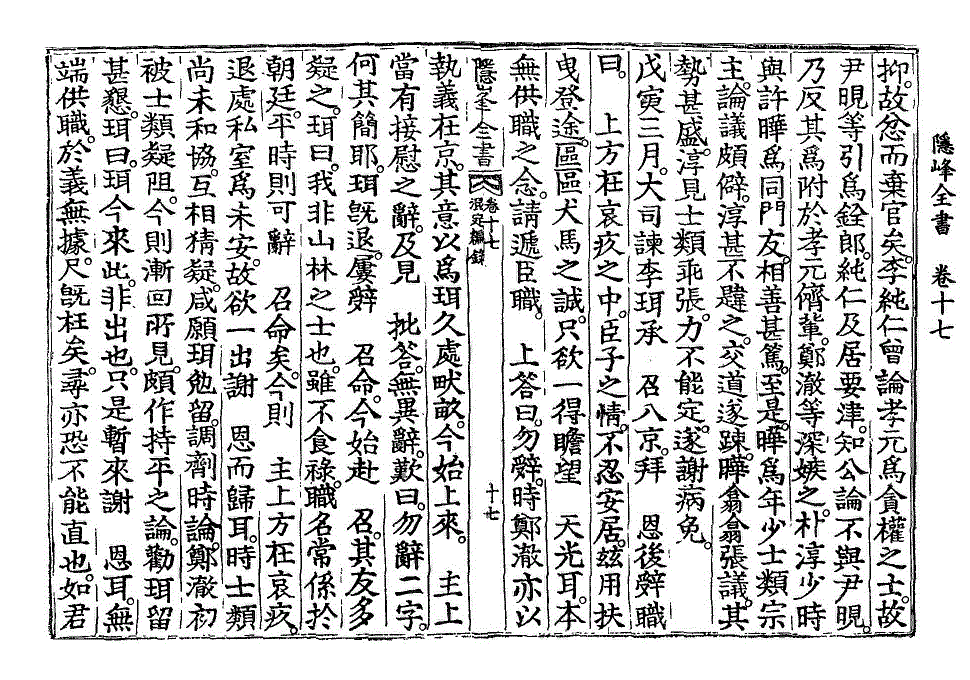 抑。故忿而弃官矣。李纯仁曾论孝元为贪权之士。故尹晛等引为铨郎。纯仁及居要津。知公论不与尹晛。乃反其为附于孝元侪辈。郑澈等深嫉之。朴淳少时与许晔为同门友。相善甚笃。至是。晔为年少士类宗主。论议颇僻。淳甚不韪之。交道遂疏。晔翕翕张议。其势甚盛。淳见士类乖张。力不能定。遂谢病免。
抑。故忿而弃官矣。李纯仁曾论孝元为贪权之士。故尹晛等引为铨郎。纯仁及居要津。知公论不与尹晛。乃反其为附于孝元侪辈。郑澈等深嫉之。朴淳少时与许晔为同门友。相善甚笃。至是。晔为年少士类宗主。论议颇僻。淳甚不韪之。交道遂疏。晔翕翕张议。其势甚盛。淳见士类乖张。力不能定。遂谢病免。戊寅三月。大司谏李珥承 召入京。拜 恩后辞职曰。 上方在哀疚之中。臣子之情。不忍安居。玆用扶曳登途。区区犬马之诚。只欲一得瞻望 天光耳。本无供职之念。请递臣职。 上答曰。勿辞。时郑澈亦以执义在京。其意以为珥久处畎亩。今始上来。 主上当有接慰之辞。及见 批答。无异辞。叹曰。勿辞二字。何其简耶。珥既退。屡辞 召命。今始赴 召。其友多疑之。珥曰。我非山林之士也。虽不食禄。职名常系于朝廷。平时则可辞 召命矣。今则 主上方在哀疚。退处私室为未安。故欲一出谢 恩而归耳。时士类尚未和协。互相猜疑。咸愿珥勉留。调剂时论。郑澈初被士类疑阻。今则渐回所见。颇作持平之论。劝珥留甚恳。珥曰。珥今来此。非出也。只是暂来谢 恩耳。无端供职。于义无据。尺既枉矣。寻亦恐不能直也。如君
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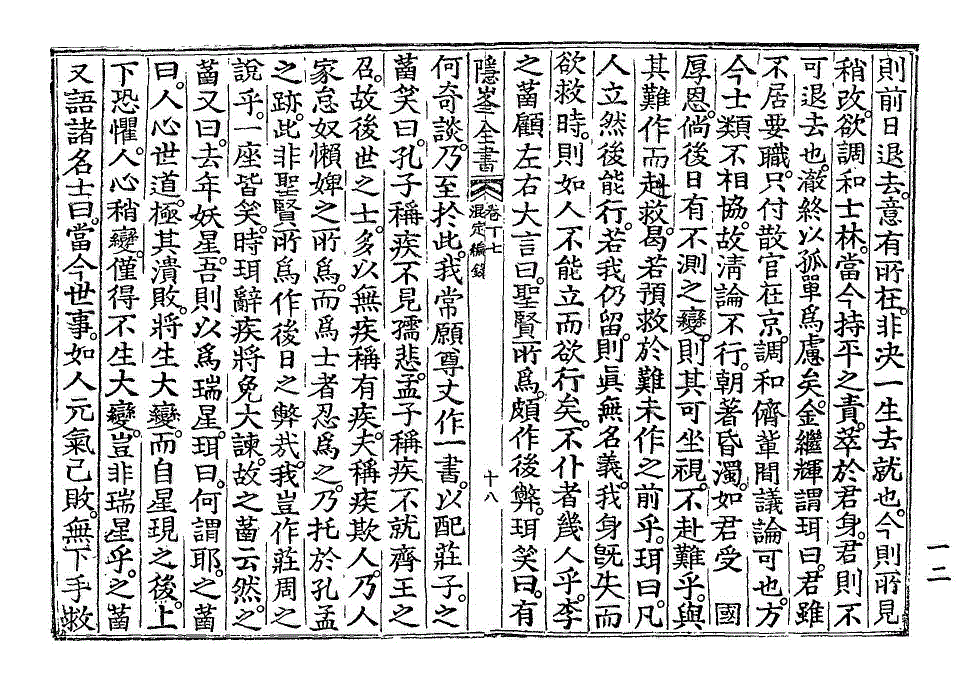 则前日退去。意有所在。非决一生去就也。今则所见稍改。欲调和士林。当今持平之责。萃于君身。君则不可退去也。澈终以孤单为虑矣。金继辉谓珥曰。君虽不居要职。只付散官在京。调和侪辈间议论可也。方今士类不相协。故清论不行。朝著昏浊。如君受 国厚恩。倘后日有不测之变。则其可坐视。不赴难乎。与其难作而赴救。曷若预救于难未作之前乎。珥曰。凡人立然后能行。若我仍留。则真无名义。我身既失而欲救时。则如人不能立而欲行矣。不仆者几人乎。李之菡顾左右大言曰。圣贤所为。颇作后弊。珥笑曰。有何奇谈。乃至于此。我常愿尊丈作一书。以配庄子。之菡笑曰。孔子称疾不见孺悲。孟子称疾不就齐王之召。故后世之士。多以无疾称有疾。夫称疾欺人。乃人家怠奴懒婢之所为。而为士者忍为之。乃托于孔孟之迹。此非圣贤所为作后日之弊哉。我岂作庄周之说乎。一座皆笑。时珥辞疾将免大谏。故之菡云然。之菡又曰。去年妖星。吾则以为瑞星。珥曰。何谓耶。之菡曰。人心世道。极其溃败。将生大变。而自星现之后。上下恐惧。人心稍变。仅得不生大变。岂非瑞星乎。之菡又语诸名士曰。当今世事。如人元气已败。无下手救
则前日退去。意有所在。非决一生去就也。今则所见稍改。欲调和士林。当今持平之责。萃于君身。君则不可退去也。澈终以孤单为虑矣。金继辉谓珥曰。君虽不居要职。只付散官在京。调和侪辈间议论可也。方今士类不相协。故清论不行。朝著昏浊。如君受 国厚恩。倘后日有不测之变。则其可坐视。不赴难乎。与其难作而赴救。曷若预救于难未作之前乎。珥曰。凡人立然后能行。若我仍留。则真无名义。我身既失而欲救时。则如人不能立而欲行矣。不仆者几人乎。李之菡顾左右大言曰。圣贤所为。颇作后弊。珥笑曰。有何奇谈。乃至于此。我常愿尊丈作一书。以配庄子。之菡笑曰。孔子称疾不见孺悲。孟子称疾不就齐王之召。故后世之士。多以无疾称有疾。夫称疾欺人。乃人家怠奴懒婢之所为。而为士者忍为之。乃托于孔孟之迹。此非圣贤所为作后日之弊哉。我岂作庄周之说乎。一座皆笑。时珥辞疾将免大谏。故之菡云然。之菡又曰。去年妖星。吾则以为瑞星。珥曰。何谓耶。之菡曰。人心世道。极其溃败。将生大变。而自星现之后。上下恐惧。人心稍变。仅得不生大变。岂非瑞星乎。之菡又语诸名士曰。当今世事。如人元气已败。无下手救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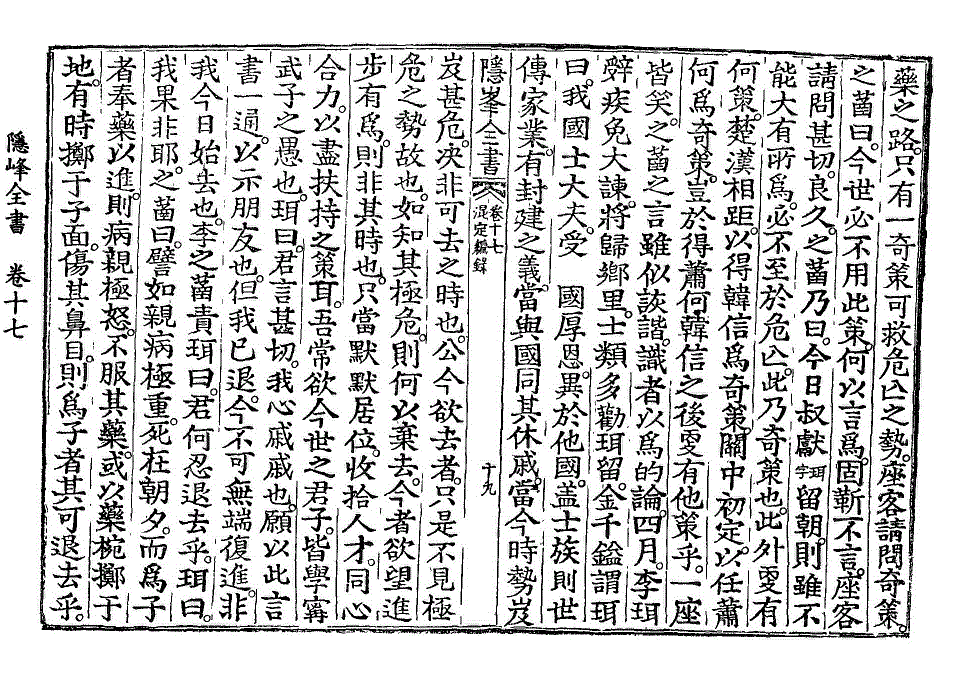 药之路。只有一奇策可救危亡之势。座客请问奇策。之菡曰。今世必不用此策。何以言为。固靳不言。座客请问甚切。良久。之菡乃曰。今日叔献(珥字)留朝。则虽不能大有所为。必不至于危亡。此乃奇策也。此外更有何策。楚汉相距。以得韩信为奇策。关中初定。以任萧何为奇策。岂于得萧何,韩信之后更有他策乎。一座皆笑。之菡之言虽似诙谐。识者以为的论。四月。李珥辞疾免大谏。将归乡里。士类多劝珥留。金千镒谓珥曰。我国士大夫。受 国厚恩。异于他国。盖士族则世传家业。有封建之义。当与国同其休戚。当今时势岌岌甚危。决非可去之时也。公今欲去者。只是不见极危之势故也。如知其极危。则何以弃去。今者欲望进步有为。则非其时也。只当默默居位。收拾人才。同心合力。以尽扶持之策耳。吾常欲今世之君子。皆学宁武子之愚也。珥曰。君言甚切。我心戚戚也。愿以此言书一通。以示朋友也。但我已退。今不可无端复进。非我今日始去也。李之菡责珥曰。君何忍退去乎。珥曰。我果非耶。之菡曰。譬如亲病极重。死在朝夕。而为子者奉药以进。则病亲极怒。不服其药。或以药碗掷于地。有时掷于子面。伤其鼻目。则为子者其可退去乎。
药之路。只有一奇策可救危亡之势。座客请问奇策。之菡曰。今世必不用此策。何以言为。固靳不言。座客请问甚切。良久。之菡乃曰。今日叔献(珥字)留朝。则虽不能大有所为。必不至于危亡。此乃奇策也。此外更有何策。楚汉相距。以得韩信为奇策。关中初定。以任萧何为奇策。岂于得萧何,韩信之后更有他策乎。一座皆笑。之菡之言虽似诙谐。识者以为的论。四月。李珥辞疾免大谏。将归乡里。士类多劝珥留。金千镒谓珥曰。我国士大夫。受 国厚恩。异于他国。盖士族则世传家业。有封建之义。当与国同其休戚。当今时势岌岌甚危。决非可去之时也。公今欲去者。只是不见极危之势故也。如知其极危。则何以弃去。今者欲望进步有为。则非其时也。只当默默居位。收拾人才。同心合力。以尽扶持之策耳。吾常欲今世之君子。皆学宁武子之愚也。珥曰。君言甚切。我心戚戚也。愿以此言书一通。以示朋友也。但我已退。今不可无端复进。非我今日始去也。李之菡责珥曰。君何忍退去乎。珥曰。我果非耶。之菡曰。譬如亲病极重。死在朝夕。而为子者奉药以进。则病亲极怒。不服其药。或以药碗掷于地。有时掷于子面。伤其鼻目。则为子者其可退去乎。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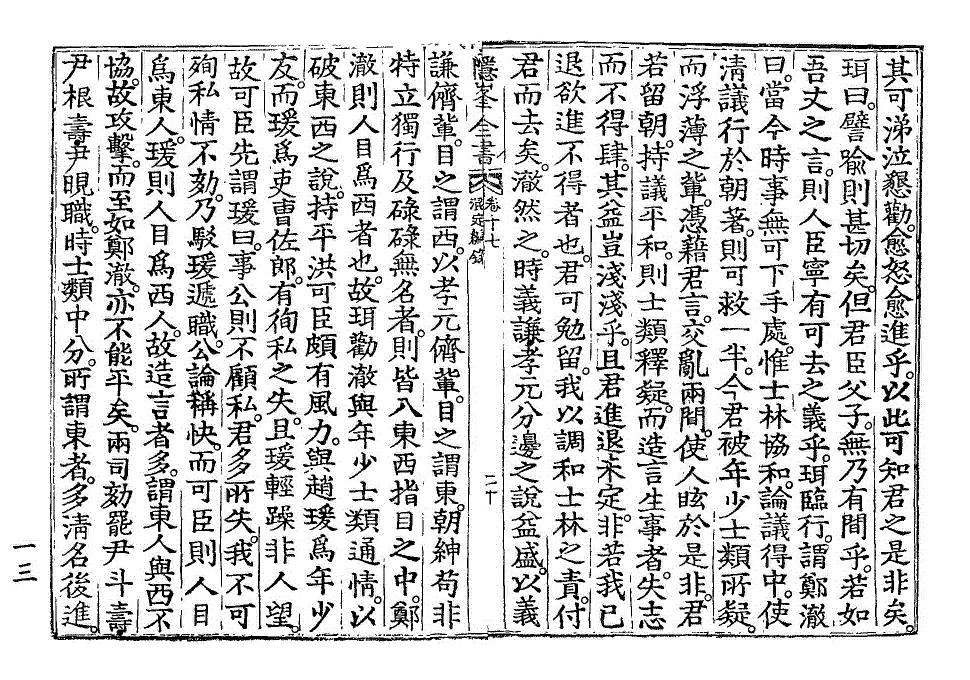 其可涕泣恳劝。愈怒愈进乎。以此可知君之是非矣。珥曰。譬喻则甚切矣。但君臣父子。无乃有间乎。若如吾丈之言。则人臣宁有可去之义乎。珥临行。谓郑澈曰。当今时事无可下手处。惟士林协和。论议得中。使清议行于朝著。则可救一半。今君被年少士类所疑。而浮薄之辈。凭藉君言。交乱两间。使人眩于是非。君若留朝。持议平和。则士类释疑。而造言生事者。失志而不得肆。其益岂浅浅乎。且君进退未定。非若我已退欲进不得者也。君可勉留。我以调和士林之责。付君而去矣。澈然之。时义谦,孝元分边之说益盛。以义谦侪辈。目之谓西。以孝元侪辈。目之谓东。朝绅苟非特立独行及碌碌无名者。则皆入东西指目之中。郑澈则人目为西者也。故珥劝澈与年少士类通情。以破东西之说。持平洪可臣颇有风力。与赵瑗为年少友。而瑗为吏曹佐郎。有徇私之失。且瑗轻躁非人望。故可臣先谓瑗曰。事公则不顾私。君多所失。我不可殉私情不劾。乃驳瑗递职。公论称快。而可臣则人目为东人。瑗则人目为西人。故造言者多。谓东人与西不协。故攻击。而至如郑澈。亦不能平矣。两司劾罢尹斗寿,尹根寿,尹晛职。时士类中分。所谓东者。多清名后进。
其可涕泣恳劝。愈怒愈进乎。以此可知君之是非矣。珥曰。譬喻则甚切矣。但君臣父子。无乃有间乎。若如吾丈之言。则人臣宁有可去之义乎。珥临行。谓郑澈曰。当今时事无可下手处。惟士林协和。论议得中。使清议行于朝著。则可救一半。今君被年少士类所疑。而浮薄之辈。凭藉君言。交乱两间。使人眩于是非。君若留朝。持议平和。则士类释疑。而造言生事者。失志而不得肆。其益岂浅浅乎。且君进退未定。非若我已退欲进不得者也。君可勉留。我以调和士林之责。付君而去矣。澈然之。时义谦,孝元分边之说益盛。以义谦侪辈。目之谓西。以孝元侪辈。目之谓东。朝绅苟非特立独行及碌碌无名者。则皆入东西指目之中。郑澈则人目为西者也。故珥劝澈与年少士类通情。以破东西之说。持平洪可臣颇有风力。与赵瑗为年少友。而瑗为吏曹佐郎。有徇私之失。且瑗轻躁非人望。故可臣先谓瑗曰。事公则不顾私。君多所失。我不可殉私情不劾。乃驳瑗递职。公论称快。而可臣则人目为东人。瑗则人目为西人。故造言者多。谓东人与西不协。故攻击。而至如郑澈。亦不能平矣。两司劾罢尹斗寿,尹根寿,尹晛职。时士类中分。所谓东者。多清名后进。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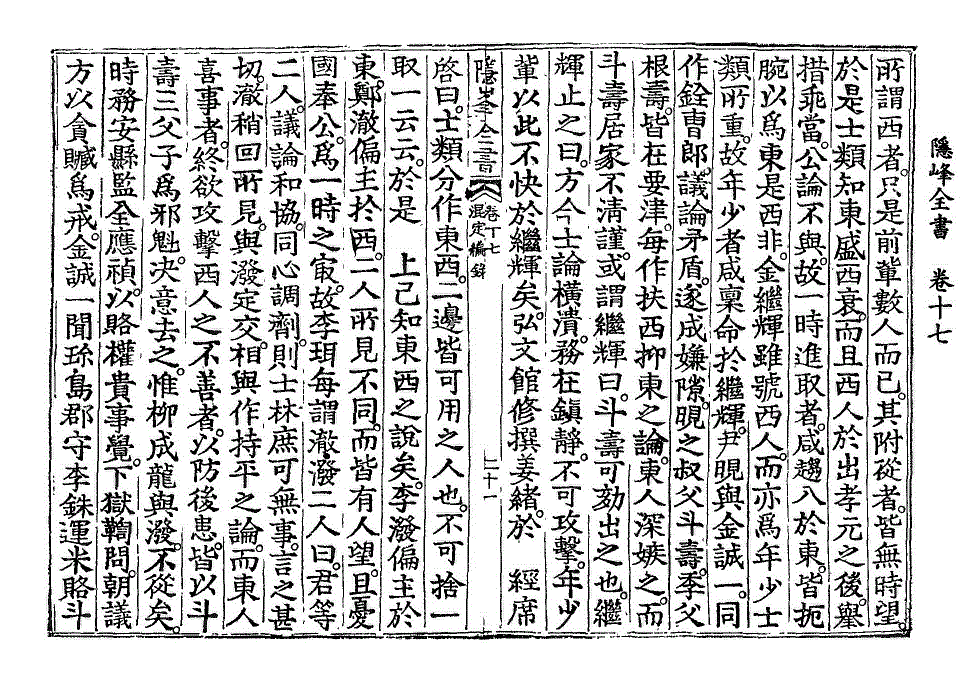 所谓西者。只是前辈数人而已。其附从者。皆无时望。于是士类知东盛西衰。而且西人于出孝元之后。举措乖当。公论不与。故一时进取者。咸趋入于东。皆扼腕以为东是西非。金继辉虽号西人。而亦为年少士类所重。故年少者咸禀命于继辉。尹晛与金诚一。同作铨曹郎。议论矛盾。遂成嫌隙。晛之叔父斗寿。季父根寿。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东之论。东人深嫉之。而斗寿居家不清谨。或谓继辉曰。斗寿可劾出之也。继辉止之曰。方今士论横溃。务在镇静。不可攻击。年少辈以此不快于继辉矣。弘文馆修撰姜绪。于 经席启曰。士类分作东西。二边皆可用之人也。不可舍一取一云云。于是 上已知东西之说矣。李泼偏主于东。郑澈偏主于西。二人所见不同。而皆有人望。且忧国奉公。为一时之最。故李珥每谓澈,泼二人曰。君等二人。议论和协。同心调剂。则士林庶可无事。言之甚切。澈稍回所见。与泼定交。相与作持平之论。而东人喜事者。终欲攻击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后患。皆以斗寿三父子为邪魁。决意去之。惟柳成龙与泼。不从矣。时务安县监全应祯。以赂权贵事觉。下狱鞫问。朝议方以贪赃为戒。金诚一闻珍岛郡守李铢运米赂斗
所谓西者。只是前辈数人而已。其附从者。皆无时望。于是士类知东盛西衰。而且西人于出孝元之后。举措乖当。公论不与。故一时进取者。咸趋入于东。皆扼腕以为东是西非。金继辉虽号西人。而亦为年少士类所重。故年少者咸禀命于继辉。尹晛与金诚一。同作铨曹郎。议论矛盾。遂成嫌隙。晛之叔父斗寿。季父根寿。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东之论。东人深嫉之。而斗寿居家不清谨。或谓继辉曰。斗寿可劾出之也。继辉止之曰。方今士论横溃。务在镇静。不可攻击。年少辈以此不快于继辉矣。弘文馆修撰姜绪。于 经席启曰。士类分作东西。二边皆可用之人也。不可舍一取一云云。于是 上已知东西之说矣。李泼偏主于东。郑澈偏主于西。二人所见不同。而皆有人望。且忧国奉公。为一时之最。故李珥每谓澈,泼二人曰。君等二人。议论和协。同心调剂。则士林庶可无事。言之甚切。澈稍回所见。与泼定交。相与作持平之论。而东人喜事者。终欲攻击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后患。皆以斗寿三父子为邪魁。决意去之。惟柳成龙与泼。不从矣。时务安县监全应祯。以赂权贵事觉。下狱鞫问。朝议方以贪赃为戒。金诚一闻珍岛郡守李铢运米赂斗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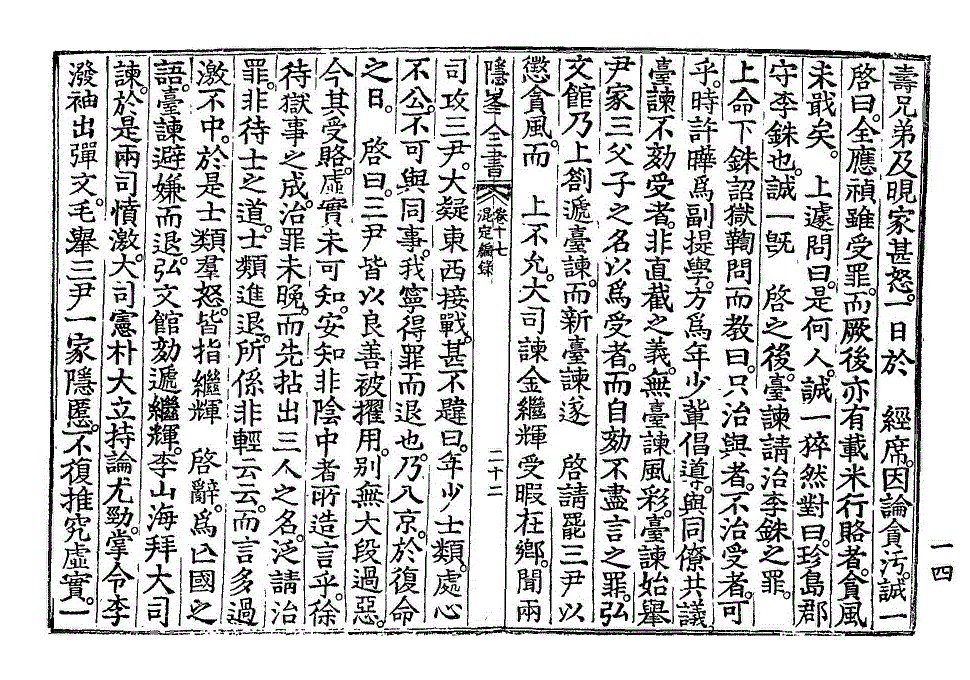 寿兄弟及晛家甚怒。一日于 经席。因论贪污。诚一启曰。全应祯虽受罪。而厥后亦有载米行赂者。贪风未戢矣。 上遽问曰。是何人。诚一猝然对曰。珍岛郡守李铢也。诚一既 启之后。台谏请治李铢之罪。 上命下铢诏狱鞫问而教曰。只治与者。不治受者。可乎。时许晔为副提学。方为年少辈倡导。与同僚共议。台谏不劾受者。非直截之义。无台谏风彩。台谏始举尹家三父子之名以为受者。而自劾不尽言之罪。弘文馆乃上劄递台谏。而新台谏遂 启请罢三尹以惩贪风。而 上不允。大司谏金继辉受暇在乡。闻两司攻三尹。大疑东西接战。甚不韪曰。年少士类。处心不公。不可与同事。我宁得罪而退也。乃入京。于复命之日。 启曰。三尹皆以良善被擢用。别无大段过恶。今其受赂。虚实未可知。安知非阴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狱事之成。治罪未晚。而先拈出三人之名。泛请治罪。非待士之道。士类进退。所系非轻云云。而言多过激不中。于是士类群怒。皆指继辉 启辞。为亡国之语。台谏避嫌而退。弘文馆劾递继辉。李山海拜大司谏。于是两司愤激。大司宪朴大立持论尤劲。掌令李泼袖出弹文。毛举三尹一家隐慝。不复推究虚实。一
寿兄弟及晛家甚怒。一日于 经席。因论贪污。诚一启曰。全应祯虽受罪。而厥后亦有载米行赂者。贪风未戢矣。 上遽问曰。是何人。诚一猝然对曰。珍岛郡守李铢也。诚一既 启之后。台谏请治李铢之罪。 上命下铢诏狱鞫问而教曰。只治与者。不治受者。可乎。时许晔为副提学。方为年少辈倡导。与同僚共议。台谏不劾受者。非直截之义。无台谏风彩。台谏始举尹家三父子之名以为受者。而自劾不尽言之罪。弘文馆乃上劄递台谏。而新台谏遂 启请罢三尹以惩贪风。而 上不允。大司谏金继辉受暇在乡。闻两司攻三尹。大疑东西接战。甚不韪曰。年少士类。处心不公。不可与同事。我宁得罪而退也。乃入京。于复命之日。 启曰。三尹皆以良善被擢用。别无大段过恶。今其受赂。虚实未可知。安知非阴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狱事之成。治罪未晚。而先拈出三人之名。泛请治罪。非待士之道。士类进退。所系非轻云云。而言多过激不中。于是士类群怒。皆指继辉 启辞。为亡国之语。台谏避嫌而退。弘文馆劾递继辉。李山海拜大司谏。于是两司愤激。大司宪朴大立持论尤劲。掌令李泼袖出弹文。毛举三尹一家隐慝。不复推究虚实。一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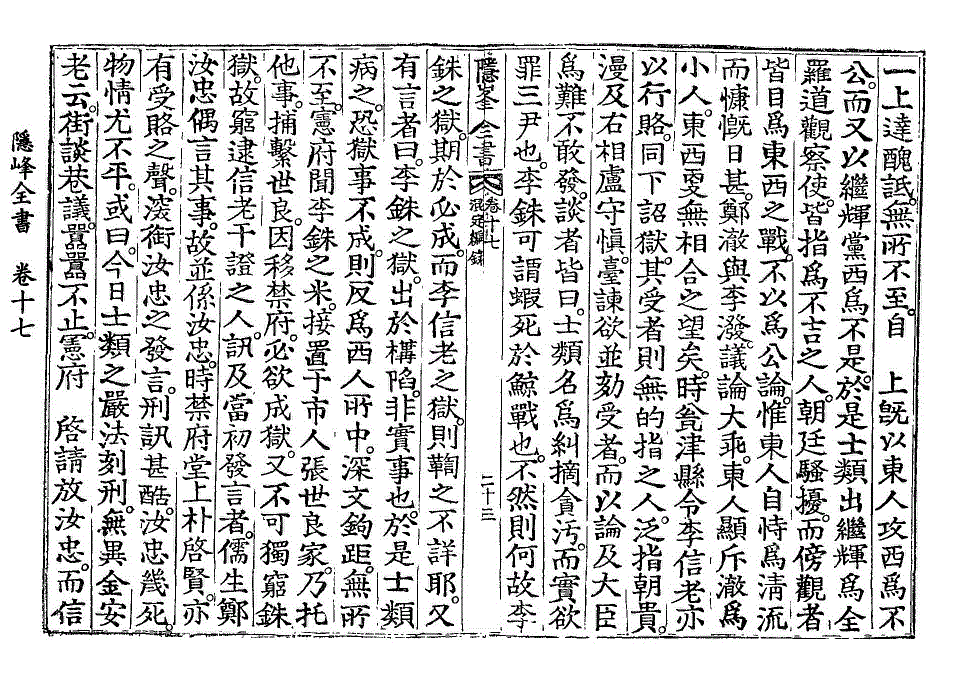 一上达丑诋。无所不至。自 上既以东人攻西为不公。而又以继辉党西为不是。于是士类出继辉为全罗道观察使。皆指为不吉之人。朝廷骚扰。而傍观者皆目为东西之战。不以为公论。惟东人自恃为清流而慷慨日甚。郑澈与李泼。议论大乖。东人显斥澈为小人。东西更无相合之望矣。时瓮津县令李信老亦以行赂。同下诏狱。其受者则无的指之人。泛指朝贵。漫及右相卢守慎。台谏欲并劾受者。而以论及大臣为难不敢发。谈者皆曰。士类名为纠摘贪污。而实欲罪三尹也。李铢可谓虾死于鲸战也。不然则何故李铢之狱。期于必成。而李信老之狱。则鞫之不详耶。又有言者曰。李铢之狱。出于构陷。非实事也。于是士类病之。恐狱事不成。则反为西人所中。深文钩距。无所不至。宪府闻李铢之米。接置于韨人张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系世良。因移禁府。必欲成狱。又不可独穷铢狱。故穷逮信老干證之人。讯及当初发言者。儒生郑汝忠偶言其事。故并系汝忠。时禁府堂上朴启贤。亦有受赂之声。深衔汝忠之发言。刑讯甚酷。汝忠几死。物情尤不平。或曰。今日士类之严法刻刑。无异金安老云。街谈巷议。嚣嚣不止。宪府 启请放汝忠。而信
一上达丑诋。无所不至。自 上既以东人攻西为不公。而又以继辉党西为不是。于是士类出继辉为全罗道观察使。皆指为不吉之人。朝廷骚扰。而傍观者皆目为东西之战。不以为公论。惟东人自恃为清流而慷慨日甚。郑澈与李泼。议论大乖。东人显斥澈为小人。东西更无相合之望矣。时瓮津县令李信老亦以行赂。同下诏狱。其受者则无的指之人。泛指朝贵。漫及右相卢守慎。台谏欲并劾受者。而以论及大臣为难不敢发。谈者皆曰。士类名为纠摘贪污。而实欲罪三尹也。李铢可谓虾死于鲸战也。不然则何故李铢之狱。期于必成。而李信老之狱。则鞫之不详耶。又有言者曰。李铢之狱。出于构陷。非实事也。于是士类病之。恐狱事不成。则反为西人所中。深文钩距。无所不至。宪府闻李铢之米。接置于韨人张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系世良。因移禁府。必欲成狱。又不可独穷铢狱。故穷逮信老干證之人。讯及当初发言者。儒生郑汝忠偶言其事。故并系汝忠。时禁府堂上朴启贤。亦有受赂之声。深衔汝忠之发言。刑讯甚酷。汝忠几死。物情尤不平。或曰。今日士类之严法刻刑。无异金安老云。街谈巷议。嚣嚣不止。宪府 启请放汝忠。而信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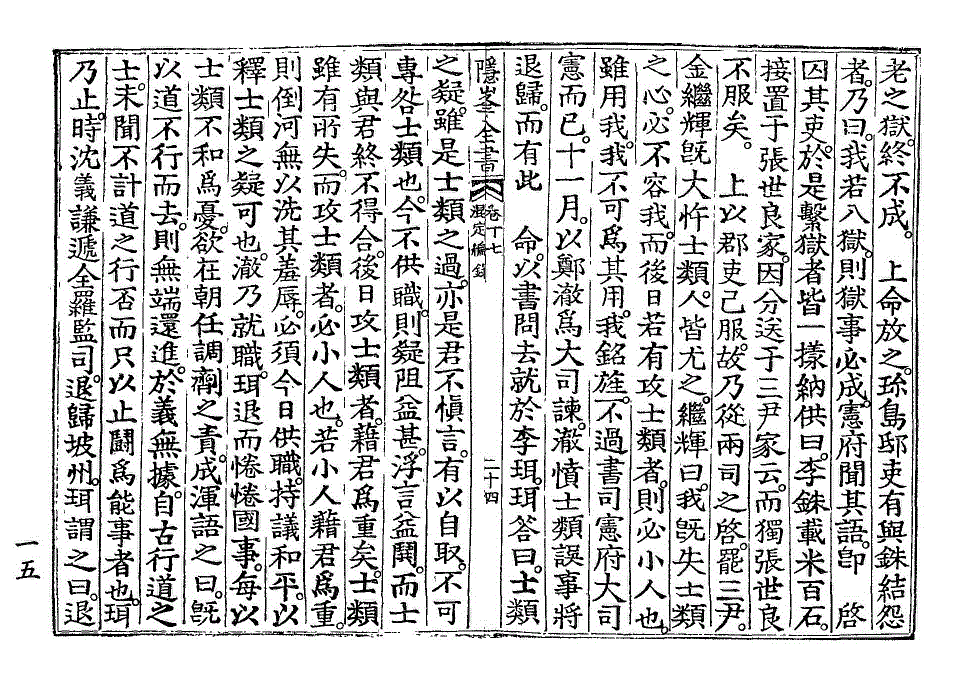 老之狱。终不成。 上命放之。珍岛邸吏有与铢结怨者。乃曰。我若入狱。则狱事必成。宪府闻其语。即 启囚其吏。于是系狱者皆一样纳供曰。李铢载米百石。接置于张世良家。因分送于三尹家云。而独张世良不服矣。 上以郡吏已服。故乃从两司之启。罢三尹。金继辉既大忤士类。人皆尤之。继辉曰。我既失士类之心。必不容我。而后日若有攻士类者。则必小人也。虽用我。我不可为其用。我铭旌。不过书司宪府大司宪而已。十一月。以郑澈为大司谏。澈愤士类误事将退归。而有此 命。以书问去就于李珥。珥答曰。士类之疑。虽是士类之过。亦是君不慎言。有以自取。不可专咎士类也。今不供职。则疑阻益甚。浮言益鬨。而士类与君终不得合。后日攻士类者。藉君为重矣。士类虽有所失。而攻士类者。必小人也。若小人藉君为重。则倒河无以洗其羞辱。必须今日供职。持议和平。以释士类之疑可也。澈乃就职。珥退而惓惓国事。每以士类不和为忧。欲在朝任调剂之责。成浑语之曰。既以道不行而去。则无端还进。于义无据。自古行道之士。未闻不计道之行否而只以止斗为能事者也。珥乃止。时沈义谦递全罗监司。退归坡州。珥谓之曰。退
老之狱。终不成。 上命放之。珍岛邸吏有与铢结怨者。乃曰。我若入狱。则狱事必成。宪府闻其语。即 启囚其吏。于是系狱者皆一样纳供曰。李铢载米百石。接置于张世良家。因分送于三尹家云。而独张世良不服矣。 上以郡吏已服。故乃从两司之启。罢三尹。金继辉既大忤士类。人皆尤之。继辉曰。我既失士类之心。必不容我。而后日若有攻士类者。则必小人也。虽用我。我不可为其用。我铭旌。不过书司宪府大司宪而已。十一月。以郑澈为大司谏。澈愤士类误事将退归。而有此 命。以书问去就于李珥。珥答曰。士类之疑。虽是士类之过。亦是君不慎言。有以自取。不可专咎士类也。今不供职。则疑阻益甚。浮言益鬨。而士类与君终不得合。后日攻士类者。藉君为重矣。士类虽有所失。而攻士类者。必小人也。若小人藉君为重。则倒河无以洗其羞辱。必须今日供职。持议和平。以释士类之疑可也。澈乃就职。珥退而惓惓国事。每以士类不和为忧。欲在朝任调剂之责。成浑语之曰。既以道不行而去。则无端还进。于义无据。自古行道之士。未闻不计道之行否而只以止斗为能事者也。珥乃止。时沈义谦递全罗监司。退归坡州。珥谓之曰。退隐峰全书卷之十七 第 16H 页
 居虽好。恐非其时。无乃益助人言乎。义谦曰。吾之退计已定。岂必避人言而自沮乎。士类既排三尹矣。若止于此。更无疑阻。则国家之幸也。若疑阻不已。名为西者。虽贤才亦不用。则举措必误矣。且如今日金显卿(贵荣字)作吏判。而三尹以贪污得罪。虽曰激浊扬清。人孰信之乎。贵荣贪鄙故云。珥曰。固然矣。士类果误矣。但士类之失。不过为搢绅之羞。而恶士类而欲治之者。其祸必重。往往亡人之国。今之时事缓急。无可恃士类。诚可忧也。义谦曰。公言是也。今之士类虽不战。容我得优游桑梓。有何忧乎后日若士类失势。则是可忧也。义谦退居未久。还朝供职。识者笑之。十二月岁抄。 恩例之下。尹斗寿三父子。皆承叙用之 命。谏官皆以为李铢狱事。时未究竟。与者方受鞫问。而受者复职。非政事之体。大司谏郑澈。独以铢狱为冤。不肯论 启。被劾而递。于是东人益诋澈为邪党矣。
居虽好。恐非其时。无乃益助人言乎。义谦曰。吾之退计已定。岂必避人言而自沮乎。士类既排三尹矣。若止于此。更无疑阻。则国家之幸也。若疑阻不已。名为西者。虽贤才亦不用。则举措必误矣。且如今日金显卿(贵荣字)作吏判。而三尹以贪污得罪。虽曰激浊扬清。人孰信之乎。贵荣贪鄙故云。珥曰。固然矣。士类果误矣。但士类之失。不过为搢绅之羞。而恶士类而欲治之者。其祸必重。往往亡人之国。今之时事缓急。无可恃士类。诚可忧也。义谦曰。公言是也。今之士类虽不战。容我得优游桑梓。有何忧乎后日若士类失势。则是可忧也。义谦退居未久。还朝供职。识者笑之。十二月岁抄。 恩例之下。尹斗寿三父子。皆承叙用之 命。谏官皆以为李铢狱事。时未究竟。与者方受鞫问。而受者复职。非政事之体。大司谏郑澈。独以铢狱为冤。不肯论 启。被劾而递。于是东人益诋澈为邪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