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x 页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疏
疏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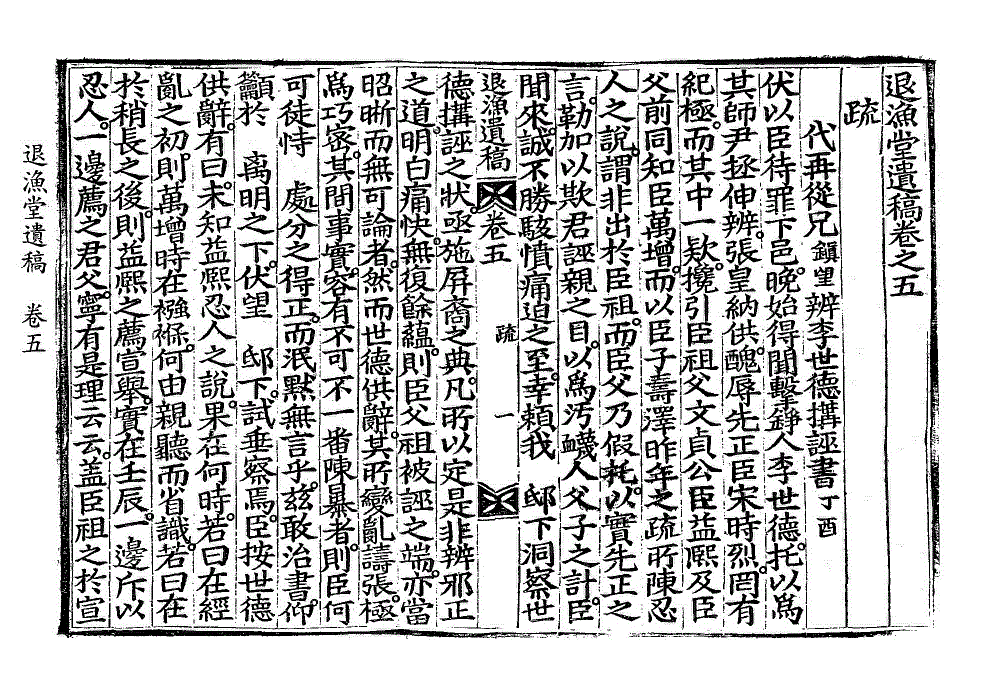 代再从兄(镇望)辨李世德搆诬书(丁酉)
代再从兄(镇望)辨李世德搆诬书(丁酉)伏以臣待罪下邑。晚始得闻击铮人李世德。托以为其师尹拯伸辨。张皇纳供。丑辱先正臣宋时烈。罔有纪极。而其中一款。搀引臣祖父文贞公臣益熙及臣父前同知臣万增。而以臣子寿泽昨年之疏所陈忍人之说。谓非出于臣祖。而臣父乃假托。以实先正之言。勒加以欺君诬亲之目。以为污蔑人父子之计。臣闻来。诚不胜骇愤痛迫之至。幸赖我 邸下洞察世德搆诬之状。亟施屏裔之典。凡所以定是非辨邪正之道。明白痛快。无复馀蕴。则臣父祖被诬之端。亦当昭晰而无可论者。然而世德供辞。其所变乱诪张。极为巧密。其间事实。容有不可不一番陈㬥者。则臣何可徒恃 处分之得正。而泯默无言乎。玆敢治书。仰吁于 离明之下。伏望 邸下。试垂察焉。臣按世德供辞。有曰。未知益熙忍人之说。果在何时。若曰在经乱之初。则万增时在襁褓。何由亲听而省识。若曰在于稍长之后。则益熙之荐宣举。实在壬辰。一边斥以忍人。一边荐之君父。宁有是理云云。盖臣祖之于宣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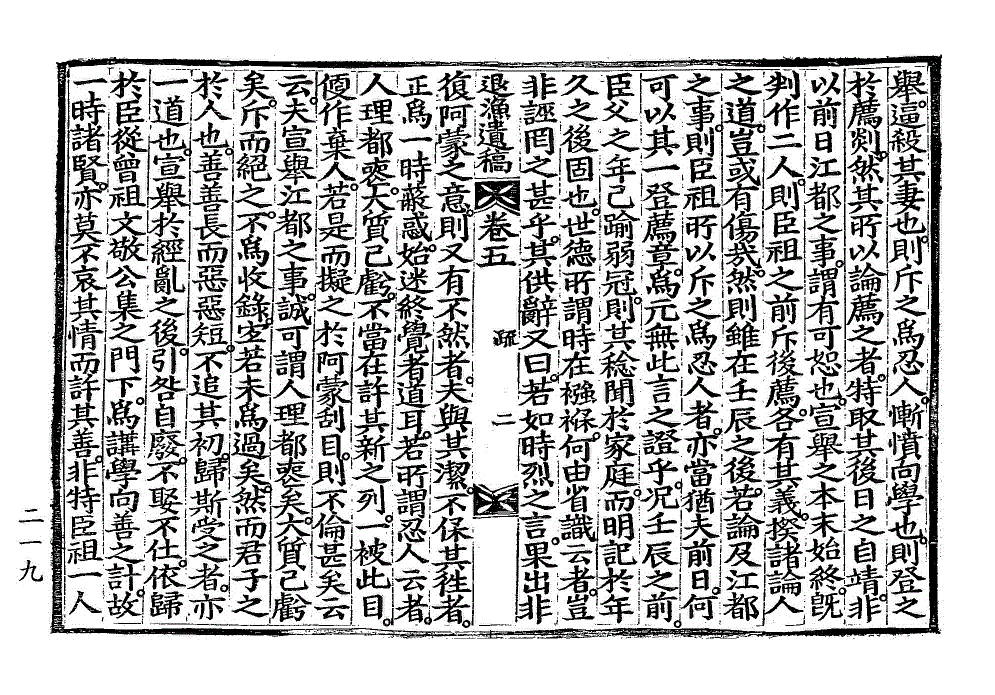 举。逼杀其妻也。则斥之为忍人。惭愤向学也。则登之于荐剡。然其所以论荐之者。特取其后日之自靖。非以前日江都之事。谓有可恕也。宣举之本末始终。既判作二人。则臣祖之前斥后荐。各有其义。揆诸论人之道。岂或有伤哉。然则虽在壬辰之后。若论及江都之事。则臣祖所以斥之为忍人者。亦当犹夫前日。何可以其一登荐章。为元无此言之證乎。况壬辰之前。臣父之年已踰弱冠。则其稔闻于家庭。而明记于年久之后固也。世德所谓时在襁褓。何由省识云者。岂非诬罔之甚乎。其供辞又曰。若如时烈之言。果出非复阿蒙之意。则又有不然者。夫与其洁。不保其往者。正为一时蔽惑。始迷终觉者道耳。若所谓忍人云者。人理都丧。大质已亏。不当在许其新之列。一被此目。便作弃人。若是而拟之于阿蒙刮目。则不伦甚矣云云。夫宣举江都之事。诚可谓人理都丧矣。大质已亏矣。斥而绝之。不为收录。宜若未为过矣。然而君子之于人也。善善长而恶恶短。不追其初。归斯受之者。亦一道也。宣举于经乱之后。引咎自废。不娶不仕。依归于臣从曾祖文敬公集之门下。为讲学向善之计。故一时诸贤。亦莫不哀其情而许其善。非特臣祖一人
举。逼杀其妻也。则斥之为忍人。惭愤向学也。则登之于荐剡。然其所以论荐之者。特取其后日之自靖。非以前日江都之事。谓有可恕也。宣举之本末始终。既判作二人。则臣祖之前斥后荐。各有其义。揆诸论人之道。岂或有伤哉。然则虽在壬辰之后。若论及江都之事。则臣祖所以斥之为忍人者。亦当犹夫前日。何可以其一登荐章。为元无此言之證乎。况壬辰之前。臣父之年已踰弱冠。则其稔闻于家庭。而明记于年久之后固也。世德所谓时在襁褓。何由省识云者。岂非诬罔之甚乎。其供辞又曰。若如时烈之言。果出非复阿蒙之意。则又有不然者。夫与其洁。不保其往者。正为一时蔽惑。始迷终觉者道耳。若所谓忍人云者。人理都丧。大质已亏。不当在许其新之列。一被此目。便作弃人。若是而拟之于阿蒙刮目。则不伦甚矣云云。夫宣举江都之事。诚可谓人理都丧矣。大质已亏矣。斥而绝之。不为收录。宜若未为过矣。然而君子之于人也。善善长而恶恶短。不追其初。归斯受之者。亦一道也。宣举于经乱之后。引咎自废。不娶不仕。依归于臣从曾祖文敬公集之门下。为讲学向善之计。故一时诸贤。亦莫不哀其情而许其善。非特臣祖一人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0H 页
 而已。则当朝廷急士之时。臣祖之荐进。只为其才之犹有可取。何可以此谓宣举以初无过失之人乎。假令臣祖有轻荐之失。其失特失之忠厚而已。世德所谓自欺欺君云者。尤岂非诬罔骇痛之甚者乎。至于故参判臣李选书。质先正之事。设使其时问答。一如世德辈所言。此亦有不可准信者。夫舍其子亲闻之语。而取实于其甥之言。断无是理。况闻两家子孙之言。其书俱不见载于家稿。而世之人亦无闻而知之者。则其间虚实。不难知矣。夫以世德辈媢嫉先正。百计搆捏。曾何所不有耶。且先正答拯书中。所谓臣祖之懑其同气之不能从容就尽者。旨意明白。本无可疑。而世德乃敢变幻兄弟喃妹。隐然为侵诬诟辱之计。此则臣之再从侄云泽。既已上书陈辨。臣故不为架叠。而如此等在人耳目灼然易知之事。犹且眩乱实状。欺罔 天聪。则其他诬饰。从可知矣。臣何足呶呶多辨乎。大抵臣祖所以斥宣举以忍人者。曾已备陈于寿泽之疏。而又有可以益明其实者。文纯公臣朴世采之抵史局书。有曰。乱初行言之溢世者。世采亦稔闻云。其行言即所谓忍人之说也。且拯之迫问先正书。有曰。追举其至情痛迫。无所归咎之语。以为
而已。则当朝廷急士之时。臣祖之荐进。只为其才之犹有可取。何可以此谓宣举以初无过失之人乎。假令臣祖有轻荐之失。其失特失之忠厚而已。世德所谓自欺欺君云者。尤岂非诬罔骇痛之甚者乎。至于故参判臣李选书。质先正之事。设使其时问答。一如世德辈所言。此亦有不可准信者。夫舍其子亲闻之语。而取实于其甥之言。断无是理。况闻两家子孙之言。其书俱不见载于家稿。而世之人亦无闻而知之者。则其间虚实。不难知矣。夫以世德辈媢嫉先正。百计搆捏。曾何所不有耶。且先正答拯书中。所谓臣祖之懑其同气之不能从容就尽者。旨意明白。本无可疑。而世德乃敢变幻兄弟喃妹。隐然为侵诬诟辱之计。此则臣之再从侄云泽。既已上书陈辨。臣故不为架叠。而如此等在人耳目灼然易知之事。犹且眩乱实状。欺罔 天聪。则其他诬饰。从可知矣。臣何足呶呶多辨乎。大抵臣祖所以斥宣举以忍人者。曾已备陈于寿泽之疏。而又有可以益明其实者。文纯公臣朴世采之抵史局书。有曰。乱初行言之溢世者。世采亦稔闻云。其行言即所谓忍人之说也。且拯之迫问先正书。有曰。追举其至情痛迫。无所归咎之语。以为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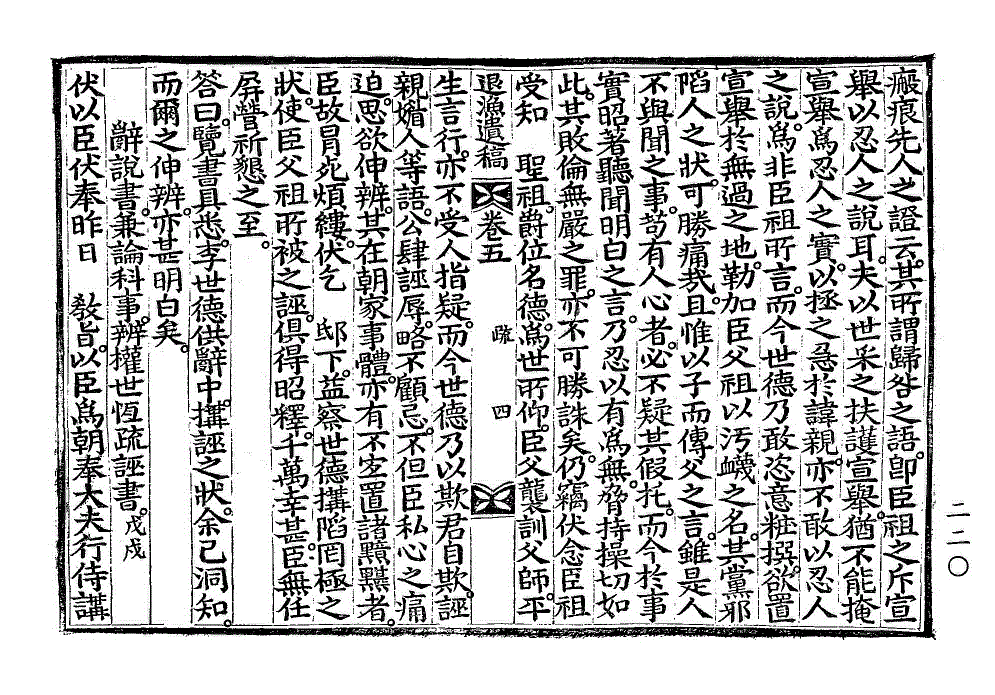 瘢痕先人之證云。其所谓归咎之语。即臣祖之斥宣举以忍人之说耳。夫以世采之扶护宣举。犹不能掩宣举为忍人之实。以拯之急于讳亲。亦不敢以忍人之说。为非臣祖所言。而今世德乃敢恣意妆撰。欲置宣举于无过之地。勒加臣父祖以污蔑之名。其党邪陷人之状。可胜痛哉。且惟以子而传父之言。虽是人不与闻之事。苟有人心者。必不疑其假托。而今于事实昭著听闻明白之言。乃忍以有为无。胁持操切如此。其败伦无严之罪。亦不可胜诛矣。仍窃伏念臣祖受知 圣祖。爵位名德。为世所仰。臣父袭训父师。平生言行。亦不受人指疑。而今世德乃以欺君自欺。诬亲媚人等语。公肆诬辱。略不顾忌。不但臣私心之痛迫。思欲伸辨。其在朝家事体。亦有不宜置诸黯黮者。臣故冒死烦缕。伏乞 邸下。益察世德搆陷罔极之状。使臣父祖所被之诬。俱得昭释。千万幸甚。臣无任屏营祈恳之至。
瘢痕先人之證云。其所谓归咎之语。即臣祖之斥宣举以忍人之说耳。夫以世采之扶护宣举。犹不能掩宣举为忍人之实。以拯之急于讳亲。亦不敢以忍人之说。为非臣祖所言。而今世德乃敢恣意妆撰。欲置宣举于无过之地。勒加臣父祖以污蔑之名。其党邪陷人之状。可胜痛哉。且惟以子而传父之言。虽是人不与闻之事。苟有人心者。必不疑其假托。而今于事实昭著听闻明白之言。乃忍以有为无。胁持操切如此。其败伦无严之罪。亦不可胜诛矣。仍窃伏念臣祖受知 圣祖。爵位名德。为世所仰。臣父袭训父师。平生言行。亦不受人指疑。而今世德乃以欺君自欺。诬亲媚人等语。公肆诬辱。略不顾忌。不但臣私心之痛迫。思欲伸辨。其在朝家事体。亦有不宜置诸黯黮者。臣故冒死烦缕。伏乞 邸下。益察世德搆陷罔极之状。使臣父祖所被之诬。俱得昭释。千万幸甚。臣无任屏营祈恳之至。答曰。览书具悉。李世德供辞中。搆诬之状。余已洞知。而尔之伸辨。亦甚明白矣。
辞说书。兼论科事。辨权世恒疏诬书。(戊戌)
伏以臣伏奉昨日 教旨。以臣为朝奉大夫行侍讲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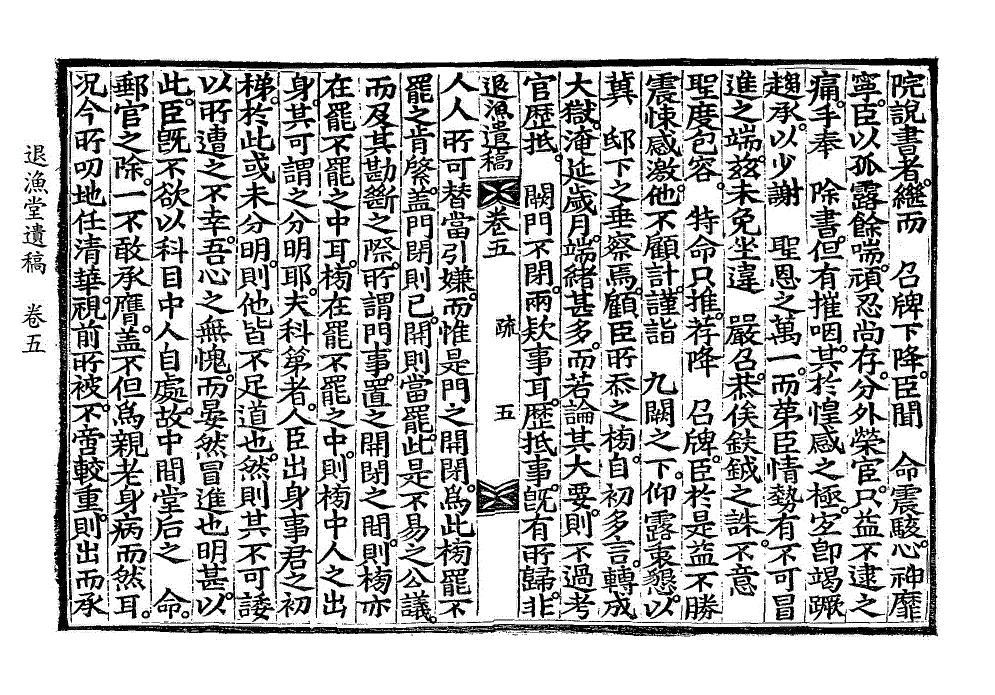 院说书者。继而 召牌下降。臣闻 命震骇。心神靡宁。臣以孤露馀喘。顽忍尚存。分外荣宦。只益不逮之痛。手奉 除书。但有摧咽。其于惶感之极。宜即竭蹶趋承。以少谢 圣恩之万一。而第臣情势有不可冒进之端。玆未免坐违 严召。恭俟鈇钺之诛。不意 圣度包容。 特命只推。荐降 召牌。臣于是益不胜震悚感激。他不顾计。谨诣 九阙之下。仰露衷恳。以冀 邸下之垂察焉。顾臣所忝之榜。自初多言。转成大狱。淹延岁月。端绪甚多。而若论其大要。则不过考官历抵。 阙门不闭。两款事耳。历抵事。既有所归。非人人所可替当引嫌。而惟是门之开闭。为此榜罢不罢之肯綮。盖门闭则已。开则当罢。此是不易之公议。而及其勘断之际。所谓门事。置之开闭之间。则榜亦在罢不罢之中耳。榜在罢不罢之中。则榜中人之出身。其可谓之分明耶。夫科第者。人臣出身事君之初梯。于此或未分明。则他皆不足道也。然则其不可诿以所遭之不幸。吾心之无愧。而晏然冒进也明甚。以此。臣既不欲以科目中人自处。故中间堂后之 命。邮官之除。一不敢承膺。盖不但为亲老身病而然耳。况今所叨地任清华。视前所被。不啻较重。则出而承
院说书者。继而 召牌下降。臣闻 命震骇。心神靡宁。臣以孤露馀喘。顽忍尚存。分外荣宦。只益不逮之痛。手奉 除书。但有摧咽。其于惶感之极。宜即竭蹶趋承。以少谢 圣恩之万一。而第臣情势有不可冒进之端。玆未免坐违 严召。恭俟鈇钺之诛。不意 圣度包容。 特命只推。荐降 召牌。臣于是益不胜震悚感激。他不顾计。谨诣 九阙之下。仰露衷恳。以冀 邸下之垂察焉。顾臣所忝之榜。自初多言。转成大狱。淹延岁月。端绪甚多。而若论其大要。则不过考官历抵。 阙门不闭。两款事耳。历抵事。既有所归。非人人所可替当引嫌。而惟是门之开闭。为此榜罢不罢之肯綮。盖门闭则已。开则当罢。此是不易之公议。而及其勘断之际。所谓门事。置之开闭之间。则榜亦在罢不罢之中耳。榜在罢不罢之中。则榜中人之出身。其可谓之分明耶。夫科第者。人臣出身事君之初梯。于此或未分明。则他皆不足道也。然则其不可诿以所遭之不幸。吾心之无愧。而晏然冒进也明甚。以此。臣既不欲以科目中人自处。故中间堂后之 命。邮官之除。一不敢承膺。盖不但为亲老身病而然耳。况今所叨地任清华。视前所被。不啻较重。则出而承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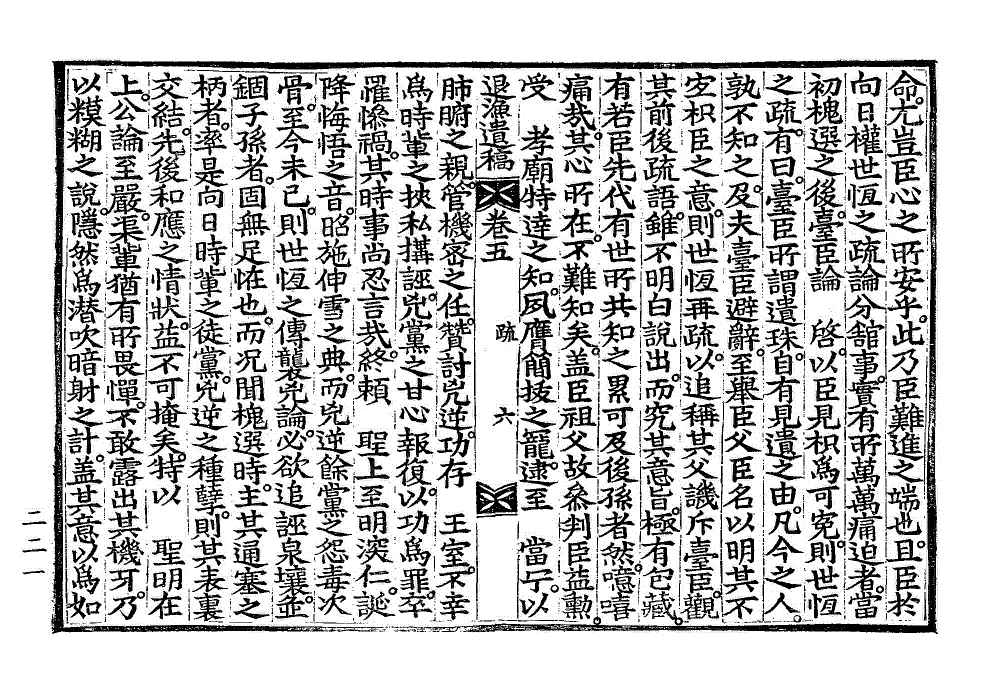 命。尤岂臣心之所安乎。此乃臣难进之端也。且臣于向日权世恒之疏论分馆事。实有所万万痛迫者。当初槐选之后。台臣论 启。以臣见枳为可冤。则世恒之疏。有曰。台臣所谓遗珠。自有见遗之由。凡今之人。孰不知之。及夫台臣避辞。至举臣父臣名以明其不宜枳臣之意。则世恒再疏。以追称其父讥斥台臣。观其前后疏语。虽不明白说出。而究其意旨。极有包藏。有若臣先代有世所共知之累可及后孙者然。噫嘻痛哉。其心所在。不难知矣。盖臣祖父故参判臣益勋。受 孝庙特达之知。夙膺简拔之宠。逮至 当宁。以肺腑之亲。管机密之任。赞讨凶逆。功存 王室。不幸为时辈之挟私搆诬。凶党之甘心报复。以功为罪。卒罹惨祸。其时事尚忍言哉。终赖 圣上至明深仁。诞降悔悟之音。昭施伸雪之典。而凶逆馀党之怨毒次骨。至今未已。则世恒之传袭凶论。必欲追诬泉壤。并锢子孙者。固无足怪也。而况闻槐选时。主其通塞之柄者。率是向日时辈之徒党。凶逆之种孽。则其表里交结。先后和应之情状。益不可掩矣。特以 圣明在上。公论至严。渠辈犹有所畏惮。不敢露出其机牙。乃以模糊之说。隐然为潜吹暗射之计。盖其意以为如
命。尤岂臣心之所安乎。此乃臣难进之端也。且臣于向日权世恒之疏论分馆事。实有所万万痛迫者。当初槐选之后。台臣论 启。以臣见枳为可冤。则世恒之疏。有曰。台臣所谓遗珠。自有见遗之由。凡今之人。孰不知之。及夫台臣避辞。至举臣父臣名以明其不宜枳臣之意。则世恒再疏。以追称其父讥斥台臣。观其前后疏语。虽不明白说出。而究其意旨。极有包藏。有若臣先代有世所共知之累可及后孙者然。噫嘻痛哉。其心所在。不难知矣。盖臣祖父故参判臣益勋。受 孝庙特达之知。夙膺简拔之宠。逮至 当宁。以肺腑之亲。管机密之任。赞讨凶逆。功存 王室。不幸为时辈之挟私搆诬。凶党之甘心报复。以功为罪。卒罹惨祸。其时事尚忍言哉。终赖 圣上至明深仁。诞降悔悟之音。昭施伸雪之典。而凶逆馀党之怨毒次骨。至今未已。则世恒之传袭凶论。必欲追诬泉壤。并锢子孙者。固无足怪也。而况闻槐选时。主其通塞之柄者。率是向日时辈之徒党。凶逆之种孽。则其表里交结。先后和应之情状。益不可掩矣。特以 圣明在上。公论至严。渠辈犹有所畏惮。不敢露出其机牙。乃以模糊之说。隐然为潜吹暗射之计。盖其意以为如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2H 页
 此。然后听者无以昭其奸。受者无以辨其诬。而渠辈可得以秘其魑魅之态。售其鬼蜮之毒故耳。其用心设计。实有至巧且密者。虽以 渊鉴所临。 离明所照。亦何以尽烛也哉。夫槐院之选。非人人之可与。如以臣为人之不合斯选。明言可枳。则夫谁曰不可。而今为黯黮囫囵之言。欲以阴伤臣祖。巧中臣身者。吁亦痛矣。呜呼。臣祖忘身为忠。受祸不悔。则到今彼辈媢嫉之言。适足以明。臣祖为国之诚。督奸之劳。其于臣祖。有何所损。而所可恨者。当此 圣君临御朝著清明之日。尚容此细人之投隙闪歘。而终不得明辨痛斥。则岂不有累于念功惩奸之典。而其为后死者之私痛。亦当如何哉。若使臣父而在。则其崩迫痛疚。当有倍于臣心。臣苟以臣父之心为心。则其可忍贪慕荣显。冒承 恩命乎。其在 朝家敦风化励廉隅之道。亦安用如此忘亲忘祖不孝无义之人哉。此尤臣难进之端也。向来一二台臣。或称臣人地。或称臣才望。是不知臣实状。而过为奖诩也。臣本庸愚谫劣。百无肖似。清选显涂。决不可忝厕。且偏母衰病。不忍暂离。痼疾缠身。不堪陈力。何莫非难冒难强者。而上款所陈情恳。固宜在谅许中。故今不暇一二胪列耳。
此。然后听者无以昭其奸。受者无以辨其诬。而渠辈可得以秘其魑魅之态。售其鬼蜮之毒故耳。其用心设计。实有至巧且密者。虽以 渊鉴所临。 离明所照。亦何以尽烛也哉。夫槐院之选。非人人之可与。如以臣为人之不合斯选。明言可枳。则夫谁曰不可。而今为黯黮囫囵之言。欲以阴伤臣祖。巧中臣身者。吁亦痛矣。呜呼。臣祖忘身为忠。受祸不悔。则到今彼辈媢嫉之言。适足以明。臣祖为国之诚。督奸之劳。其于臣祖。有何所损。而所可恨者。当此 圣君临御朝著清明之日。尚容此细人之投隙闪歘。而终不得明辨痛斥。则岂不有累于念功惩奸之典。而其为后死者之私痛。亦当如何哉。若使臣父而在。则其崩迫痛疚。当有倍于臣心。臣苟以臣父之心为心。则其可忍贪慕荣显。冒承 恩命乎。其在 朝家敦风化励廉隅之道。亦安用如此忘亲忘祖不孝无义之人哉。此尤臣难进之端也。向来一二台臣。或称臣人地。或称臣才望。是不知臣实状。而过为奖诩也。臣本庸愚谫劣。百无肖似。清选显涂。决不可忝厕。且偏母衰病。不忍暂离。痼疾缠身。不堪陈力。何莫非难冒难强者。而上款所陈情恳。固宜在谅许中。故今不暇一二胪列耳。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2L 页
 噫。人之所贵乎科第者。盖以荣其身显其先故也。在臣则不惟不能荣显而已。不过为污身名辱祖先之资。俯仰惭痛。尚谁尤哉。为今之计。惟有退伏循省。息念从宦。庶可以安分而自靖。耿耿此心。可质神明。 离照所及。岂不下烛。伏乞 邸下。察臣情迹不可冒进。亟将新授职名。为先镌改。仍 命有司。治臣慢蹇渎扰之罪。以警具僚。千万幸甚。臣无任惕慄恳迫祈祝颙俟之至。
噫。人之所贵乎科第者。盖以荣其身显其先故也。在臣则不惟不能荣显而已。不过为污身名辱祖先之资。俯仰惭痛。尚谁尤哉。为今之计。惟有退伏循省。息念从宦。庶可以安分而自靖。耿耿此心。可质神明。 离照所及。岂不下烛。伏乞 邸下。察臣情迹不可冒进。亟将新授职名。为先镌改。仍 命有司。治臣慢蹇渎扰之罪。以警具僚。千万幸甚。臣无任惕慄恳迫祈祝颙俟之至。答曰。览书具悉。科事已行查明。权世恒疏语。殊甚谬戾。俱无可嫌。尔其勿辞。从速察职。
移拜注书辨韩祉搆诬书
伏以臣于向日政。有移拜堂后之 命。前授未递而新 除荐加。罪戾日积而 恩眷愈重。臣诚惶陨感激。罔知攸措。此际得见韩祉书本。以臣向日辞章中时辈挟私搆诬之语。谓有所指斥于其父泰东。大加狠怒。丑辱臣祖父故参判臣益勋。罔有纪极。遣言造意。至憯且毒。臣于是骇愤痛迫。直欲无生。仰惟 渊鉴下临。 离辉旁照。其于臣祖诬冤之端。祉之搆捏之状。宜无不洞烛。而第念事在久远。其间委折。容有所未及俯悉者。则臣何可徒恃 临照之明。而泯默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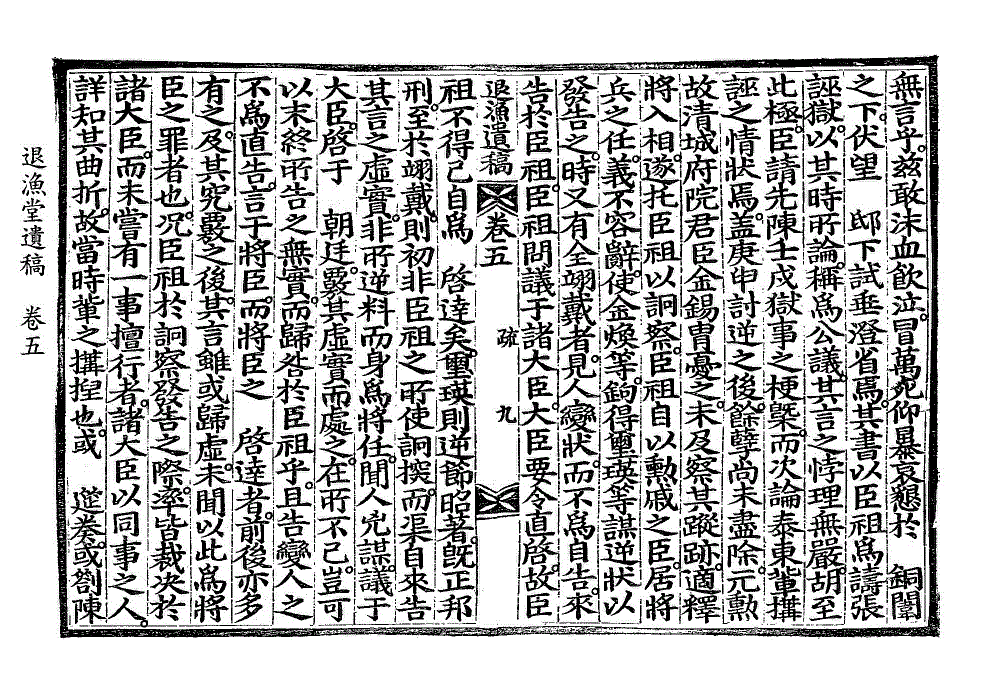 无言乎。玆敢沬血饮泣。冒万死仰㬥哀恳于 铜闱之下。伏望 邸下试垂澄省焉。其书以臣祖为诪张诬狱。以其时所论。称为公议。其言之悖理无严。胡至此极。臣请先陈壬戌狱事之梗槩。而次论泰东辈搆诬之情状焉。盖庚申讨逆之后。馀孽尚未尽除。元勋故清城府院君臣金锡胄忧之。未及察其踪迹。适释将入相。遂托臣祖以诇察。臣祖自以勋戚之臣。居将兵之任。义不容辞。使金焕等。钩得玺瑛等谋逆状以发告之。时又有全翊戴者。见人变状。而不为自告。来告于臣祖。臣祖问议于诸大臣。大臣要令直启。故臣祖不得已自为 启达矣。玺瑛则逆节昭著。既正邦刑。至于翊戴。则初非臣祖之所使诇探。而渠自来告其言之虚实。非所逆料而身为将任。闻人凶谋。议于大臣。启于 朝廷。覈其虚实而处之。在所不已。岂可以末终所告之无实。而归咎于臣祖乎。且告变人之不为直告。言于将臣。而将臣之 启达者。前后亦多有之。及其究覈之后。其言虽或归虚。未闻以此为将臣之罪者也。况臣祖于诇察发告之际。率皆裁决于诸大臣。而未尝有一事擅行者。诸大臣以同事之人。详知其曲折。故当时辈之搆捏也。或 筵奏。或劄陈
无言乎。玆敢沬血饮泣。冒万死仰㬥哀恳于 铜闱之下。伏望 邸下试垂澄省焉。其书以臣祖为诪张诬狱。以其时所论。称为公议。其言之悖理无严。胡至此极。臣请先陈壬戌狱事之梗槩。而次论泰东辈搆诬之情状焉。盖庚申讨逆之后。馀孽尚未尽除。元勋故清城府院君臣金锡胄忧之。未及察其踪迹。适释将入相。遂托臣祖以诇察。臣祖自以勋戚之臣。居将兵之任。义不容辞。使金焕等。钩得玺瑛等谋逆状以发告之。时又有全翊戴者。见人变状。而不为自告。来告于臣祖。臣祖问议于诸大臣。大臣要令直启。故臣祖不得已自为 启达矣。玺瑛则逆节昭著。既正邦刑。至于翊戴。则初非臣祖之所使诇探。而渠自来告其言之虚实。非所逆料而身为将任。闻人凶谋。议于大臣。启于 朝廷。覈其虚实而处之。在所不已。岂可以末终所告之无实。而归咎于臣祖乎。且告变人之不为直告。言于将臣。而将臣之 启达者。前后亦多有之。及其究覈之后。其言虽或归虚。未闻以此为将臣之罪者也。况臣祖于诇察发告之际。率皆裁决于诸大臣。而未尝有一事擅行者。诸大臣以同事之人。详知其曲折。故当时辈之搆捏也。或 筵奏。或劄陈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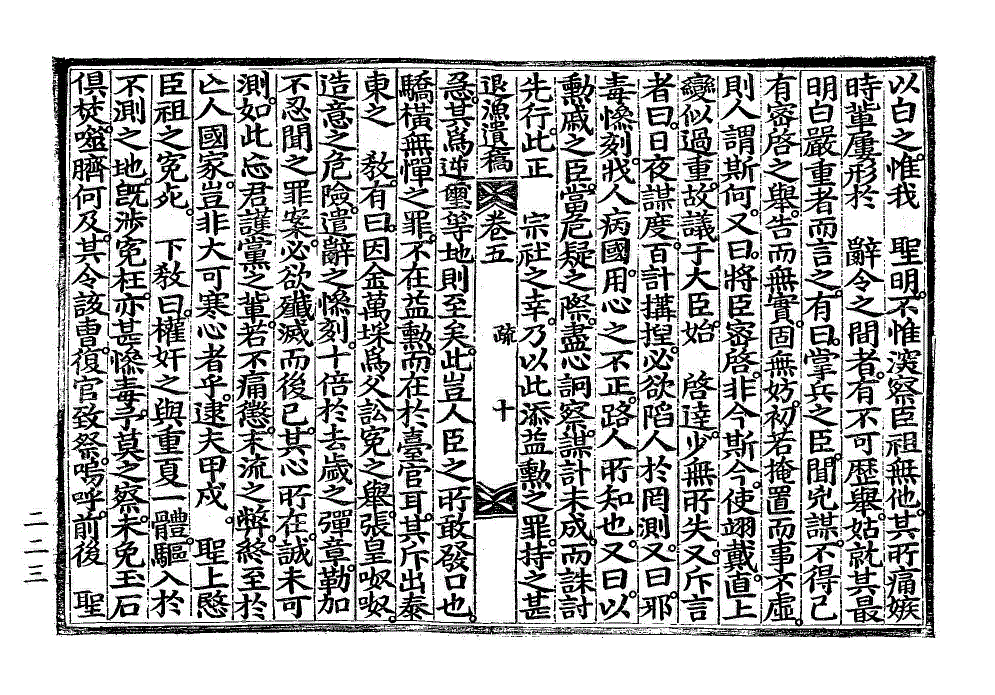 以白之。惟我 圣明。不惟深察臣祖无他。其所痛嫉时辈屡形于 辞令之间者。有不可历举。姑就其最明白严重者而言之。有曰。掌兵之臣。闻凶谋。不得已有密启之举。告而无实。固无妨。初若掩置而事不虚。则人谓斯何。又曰。将臣密启。非今斯今。使翊戴。直上变似过重。故议于大臣。始 启达。少无所失。又斥言者曰。日夜谋度。百计搆捏。必欲陷人于罔测。又曰。邪毒惨刻。戕人病国。用心之不正。路人所知也。又曰。以勋戚之臣。当危疑之际。尽心诇察。谋计未成。而诛讨先行。此正 宗社之幸。乃以此添益勋之罪。持之甚急。其为逆玺等地则至矣。此岂人臣之所敢发口也。骄横无惮之罪。不在益勋。而在于台官耳。其斥出泰东之 教。有曰。因金万埰为父讼冤之举。张皇呶呶。造意之危险。遣辞之惨刻。十倍于去岁之弹章。勒加不忍闻之罪案。必欲歼灭而后已。其心所在。诚未可测。如此忘君护党之辈。若不痛惩。末流之弊。终至于亡人国家。岂非大可寒心者乎。逮夫甲戌。 圣上悯臣祖之冤死。 下教曰。权奸之与重夏一体。驱入于不测之地。既涉冤枉。亦甚惨毒。予莫之察。未免玉石俱焚。噬脐何及。其令该曹。复官致祭。呜呼。前后 圣
以白之。惟我 圣明。不惟深察臣祖无他。其所痛嫉时辈屡形于 辞令之间者。有不可历举。姑就其最明白严重者而言之。有曰。掌兵之臣。闻凶谋。不得已有密启之举。告而无实。固无妨。初若掩置而事不虚。则人谓斯何。又曰。将臣密启。非今斯今。使翊戴。直上变似过重。故议于大臣。始 启达。少无所失。又斥言者曰。日夜谋度。百计搆捏。必欲陷人于罔测。又曰。邪毒惨刻。戕人病国。用心之不正。路人所知也。又曰。以勋戚之臣。当危疑之际。尽心诇察。谋计未成。而诛讨先行。此正 宗社之幸。乃以此添益勋之罪。持之甚急。其为逆玺等地则至矣。此岂人臣之所敢发口也。骄横无惮之罪。不在益勋。而在于台官耳。其斥出泰东之 教。有曰。因金万埰为父讼冤之举。张皇呶呶。造意之危险。遣辞之惨刻。十倍于去岁之弹章。勒加不忍闻之罪案。必欲歼灭而后已。其心所在。诚未可测。如此忘君护党之辈。若不痛惩。末流之弊。终至于亡人国家。岂非大可寒心者乎。逮夫甲戌。 圣上悯臣祖之冤死。 下教曰。权奸之与重夏一体。驱入于不测之地。既涉冤枉。亦甚惨毒。予莫之察。未免玉石俱焚。噬脐何及。其令该曹。复官致祭。呜呼。前后 圣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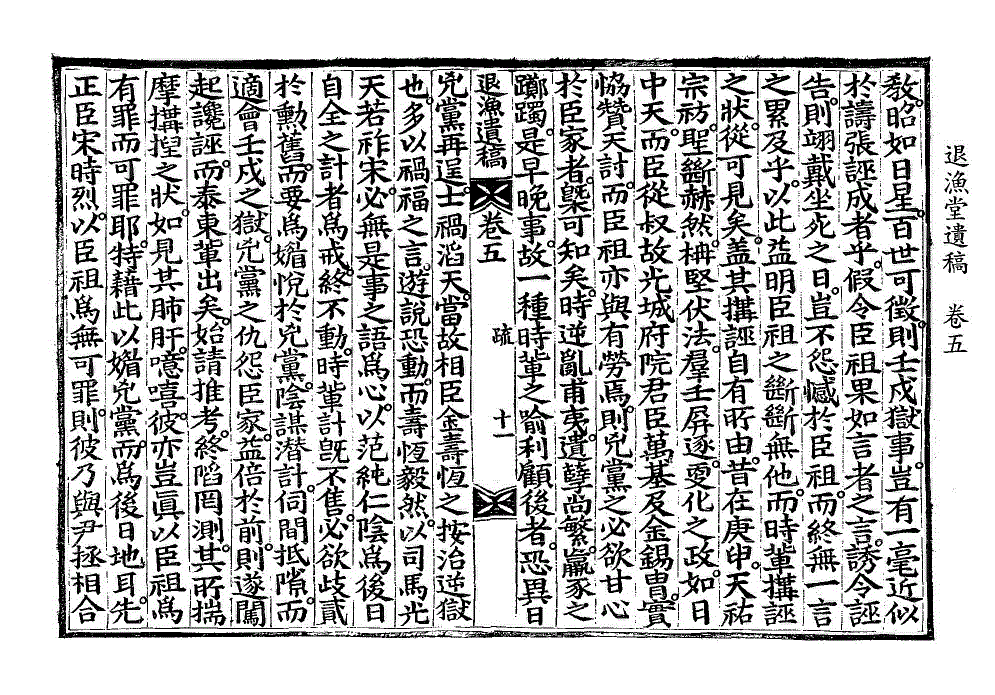 教。昭如日星。百世可徵。则壬戌狱事。岂有一毫近似于诪张诬成者乎。假令臣祖果如言者之言。诱令诬告。则翊戴坐死之日。岂不怨憾于臣祖。而终无一言之累及乎。以此益明臣祖之断断无他。而时辈搆诬之状。从可见矣。盖其搆诬自有所由。昔在庚申。天祐宗祊。圣断赫然。楠坚伏法。群壬屏逐。更化之政。如日中天。而臣从叔故光城府院君臣万基及金锡胄。实协赞天讨。而臣祖亦与有劳焉。则凶党之必欲甘心于臣家者。槩可知矣。时逆乱甫夷。遗孽尚繁。羸豕之踯躅。是早晚事。故一种时辈之喻利顾后者。恐异日凶党再逞。士祸滔天。当故相臣金寿恒之按治逆狱也。多以祸福之言。游说恐动。而寿恒毅然。以司马光天若祚宋。必无是事之语为心。以范纯仁阴为后日自全之计者为戒。终不动。时辈计既不售。必欲歧贰于勋旧。而要为媚悦于凶党。阴谋潜计。伺间抵隙。而适会壬戌之狱。凶党之仇怨臣家。益倍于前。则遂闯起谗诬。而泰东辈出矣。始请推考。终陷罔测。其所揣摩搆捏之状。如见其肺肝。噫嘻。彼亦岂真以臣祖为有罪而可罪耶。特藉此以媚凶党。而为后日地耳。先正臣宋时烈。以臣祖为无可罪。则彼乃与尹拯相合
教。昭如日星。百世可徵。则壬戌狱事。岂有一毫近似于诪张诬成者乎。假令臣祖果如言者之言。诱令诬告。则翊戴坐死之日。岂不怨憾于臣祖。而终无一言之累及乎。以此益明臣祖之断断无他。而时辈搆诬之状。从可见矣。盖其搆诬自有所由。昔在庚申。天祐宗祊。圣断赫然。楠坚伏法。群壬屏逐。更化之政。如日中天。而臣从叔故光城府院君臣万基及金锡胄。实协赞天讨。而臣祖亦与有劳焉。则凶党之必欲甘心于臣家者。槩可知矣。时逆乱甫夷。遗孽尚繁。羸豕之踯躅。是早晚事。故一种时辈之喻利顾后者。恐异日凶党再逞。士祸滔天。当故相臣金寿恒之按治逆狱也。多以祸福之言。游说恐动。而寿恒毅然。以司马光天若祚宋。必无是事之语为心。以范纯仁阴为后日自全之计者为戒。终不动。时辈计既不售。必欲歧贰于勋旧。而要为媚悦于凶党。阴谋潜计。伺间抵隙。而适会壬戌之狱。凶党之仇怨臣家。益倍于前。则遂闯起谗诬。而泰东辈出矣。始请推考。终陷罔测。其所揣摩搆捏之状。如见其肺肝。噫嘻。彼亦岂真以臣祖为有罪而可罪耶。特藉此以媚凶党。而为后日地耳。先正臣宋时烈。以臣祖为无可罪。则彼乃与尹拯相合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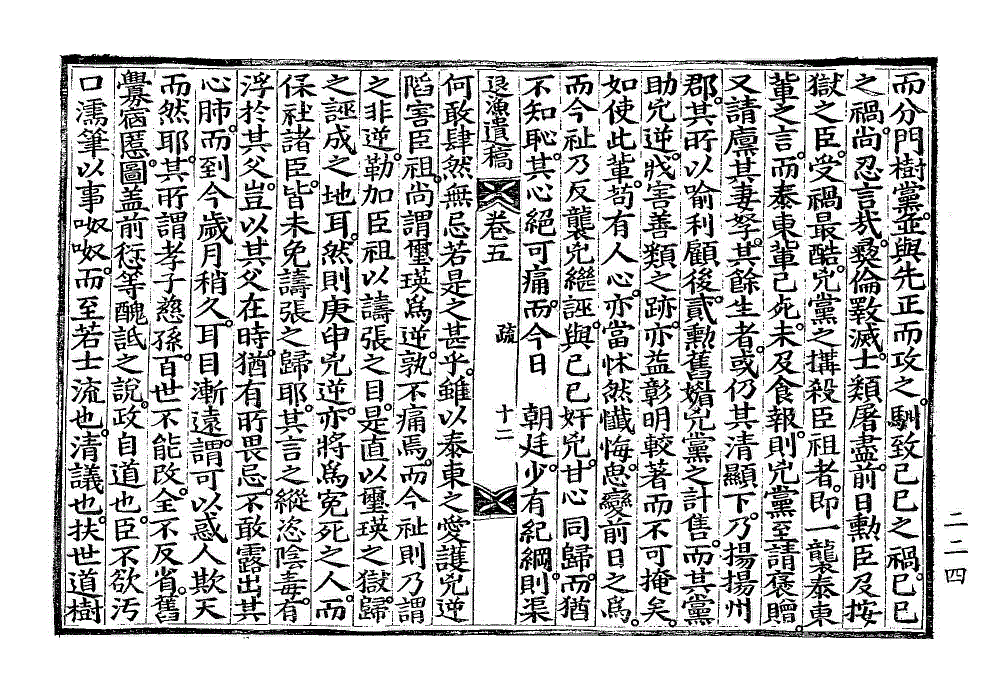 而分门树党。并与先正而攻之。驯致己巳之祸。己巳之祸。尚忍言哉。彝伦斁灭。士类屠尽。前日勋臣及按狱之臣。受祸最酷。凶党之搆杀臣祖者。即一袭泰东辈之言。而泰东辈已死。未及食报。则凶党至请褒赠。又请廪其妻孥。其馀生者。或仍其清显下。乃扬扬州郡。其所以喻利顾后。贰勋旧媚凶党之计售。而其党助凶逆。戕害善类之迹。亦益彰明较著而不可掩矣。如使此辈。苟有人心。亦当怵然忏悔。思变前日之为。而今祉乃反袭凶继诬。与己巳奸凶。甘心同归。而犹不知耻。其心绝可痛。而今日 朝廷。少有纪纲。则渠何敢肆然无忌若是之甚乎。虽以泰东之爱护凶逆陷害臣祖。尚谓玺瑛为逆。孰不痛焉。而今祉则乃谓之非逆。勒加臣祖以诪张之目。是直以玺瑛之狱。归之诬成之地耳。然则庚申凶逆。亦将为冤死之人。而保社诸臣。皆未免诪张之归耶。其言之纵恣阴毒。有浮于其父。岂以其父在时。犹有所畏忌。不敢露出其心肺。而到今岁月稍久。耳目渐远。谓可以惑人欺天而然耶。其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全不反省。旧衅宿慝。图盖前愆等丑诋之说。政自道也。臣不欲污口濡笔以事呶呶。而至若士流也。清议也。扶世道树
而分门树党。并与先正而攻之。驯致己巳之祸。己巳之祸。尚忍言哉。彝伦斁灭。士类屠尽。前日勋臣及按狱之臣。受祸最酷。凶党之搆杀臣祖者。即一袭泰东辈之言。而泰东辈已死。未及食报。则凶党至请褒赠。又请廪其妻孥。其馀生者。或仍其清显下。乃扬扬州郡。其所以喻利顾后。贰勋旧媚凶党之计售。而其党助凶逆。戕害善类之迹。亦益彰明较著而不可掩矣。如使此辈。苟有人心。亦当怵然忏悔。思变前日之为。而今祉乃反袭凶继诬。与己巳奸凶。甘心同归。而犹不知耻。其心绝可痛。而今日 朝廷。少有纪纲。则渠何敢肆然无忌若是之甚乎。虽以泰东之爱护凶逆陷害臣祖。尚谓玺瑛为逆。孰不痛焉。而今祉则乃谓之非逆。勒加臣祖以诪张之目。是直以玺瑛之狱。归之诬成之地耳。然则庚申凶逆。亦将为冤死之人。而保社诸臣。皆未免诪张之归耶。其言之纵恣阴毒。有浮于其父。岂以其父在时。犹有所畏忌。不敢露出其心肺。而到今岁月稍久。耳目渐远。谓可以惑人欺天而然耶。其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全不反省。旧衅宿慝。图盖前愆等丑诋之说。政自道也。臣不欲污口濡笔以事呶呶。而至若士流也。清议也。扶世道树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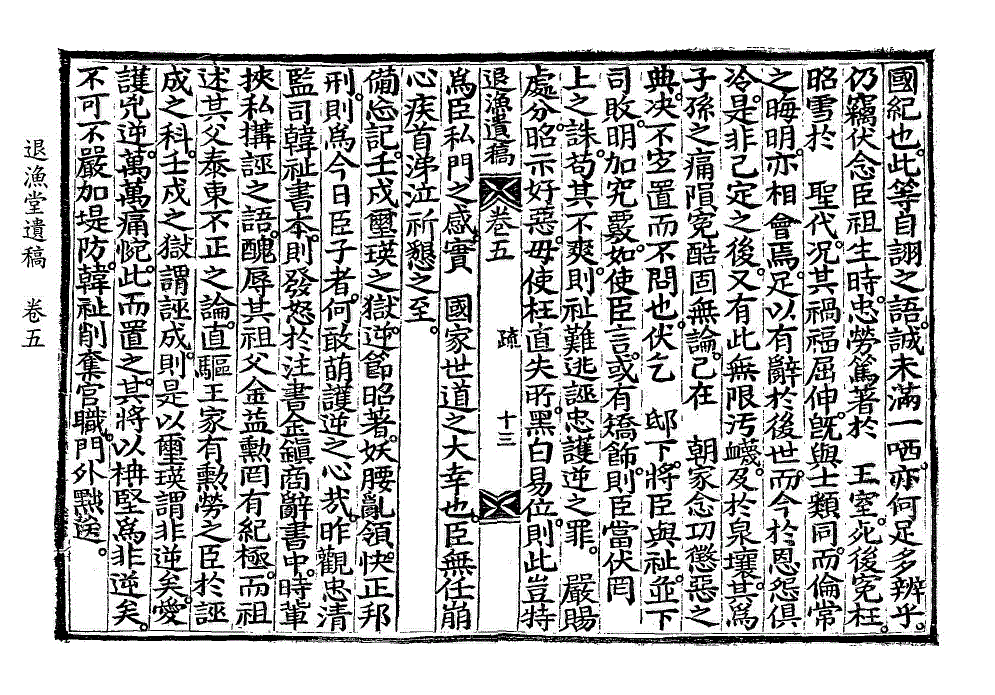 国纪也。此等自诩之语。诚未满一哂。亦何足多辨乎。仍窃伏念臣祖生时。忠劳笃著于 王室。死后冤枉。昭雪于 圣代。况其祸福屈伸。既与士类同。而伦常之晦明。亦相会焉。足以有辞于后世。而今于恩怨俱冷。是非已定之后。又有此无限污蔑。及于泉壤。其为子孙之痛陨冤酷固无论。已在 朝家念功惩恶之典。决不宜置而不问也。伏乞 邸下。将臣与祉。并下司败。明加究覈。如使臣言。或有矫饰。则臣当伏罔 上之诛。苟其不爽。则祉难逃诬忠护逆之罪。 严赐处分。昭示好恶。毋使枉直失所。黑白易位。则此岂特为臣私门之感。实 国家世道之大幸也。臣无任崩心疾首涕泣祈恳之至。
国纪也。此等自诩之语。诚未满一哂。亦何足多辨乎。仍窃伏念臣祖生时。忠劳笃著于 王室。死后冤枉。昭雪于 圣代。况其祸福屈伸。既与士类同。而伦常之晦明。亦相会焉。足以有辞于后世。而今于恩怨俱冷。是非已定之后。又有此无限污蔑。及于泉壤。其为子孙之痛陨冤酷固无论。已在 朝家念功惩恶之典。决不宜置而不问也。伏乞 邸下。将臣与祉。并下司败。明加究覈。如使臣言。或有矫饰。则臣当伏罔 上之诛。苟其不爽。则祉难逃诬忠护逆之罪。 严赐处分。昭示好恶。毋使枉直失所。黑白易位。则此岂特为臣私门之感。实 国家世道之大幸也。臣无任崩心疾首涕泣祈恳之至。备忘记。壬戌玺瑛之狱。逆节昭著。妖腰乱领。快正邦刑。则为今日臣子者。何敢萌护逆之心哉。昨观忠清监司韩祉书本。则发怒于注书金镇商辞书中。时辈挟私搆诬之语。丑辱其祖父金益勋罔有纪极。而祖述其父泰东不正之论。直驱王家有勋劳之臣于诬成之科。壬戌之狱谓诬成。则是以玺瑛谓非逆矣。爱护凶逆。万万痛惋。此而置之。其将以楠,坚为非逆矣。不可不严加堤防。韩祉削夺官职。门外黜送。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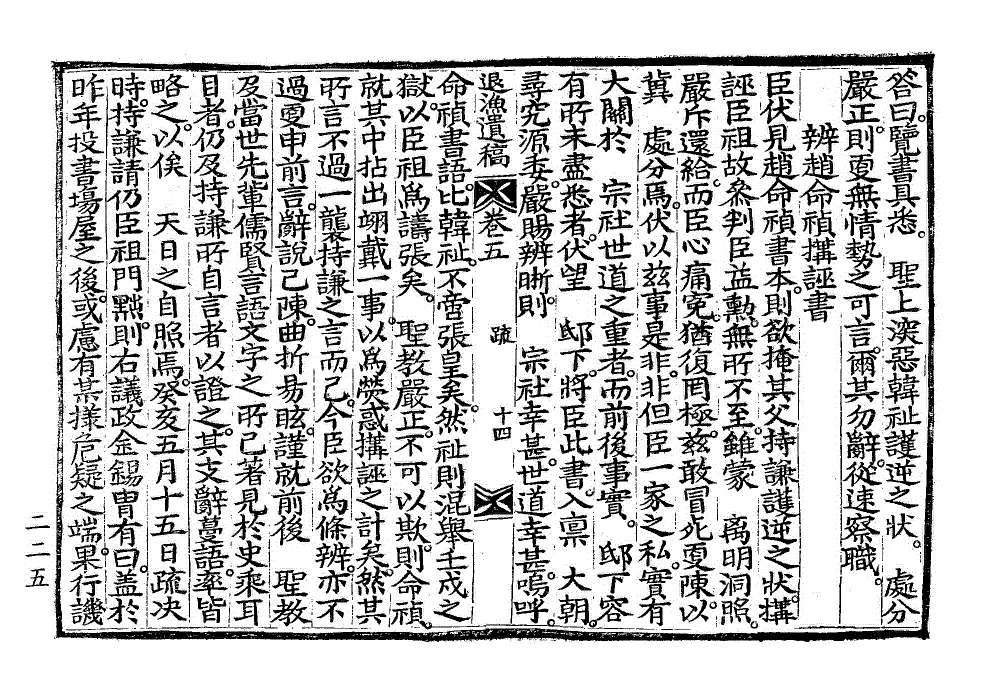 答曰。览书具悉。 圣上深恶韩祉护逆之状。 处分严正。则更无情势之可言。尔其勿辞。从速察职。
答曰。览书具悉。 圣上深恶韩祉护逆之状。 处分严正。则更无情势之可言。尔其勿辞。从速察职。辨赵命祯搆诬书
臣伏见赵命祯书本。则欲掩其父持谦护逆之状。搆诬臣祖故参判臣益勋。无所不至。虽蒙 离明洞照。严斥还给。而臣心痛冤。犹复罔极。玆敢冒死更陈。以冀 处分焉。伏以玆事是非。非但臣一家之私。实有大关于 宗社世道之重者。而前后事实。 邸下容有所未尽悉者。伏望 邸下。将臣此书。入禀 大朝。寻究源委。严赐辨晰。则 宗社幸甚。世道幸甚。呜呼。命祯书语。比韩祉。不啻张皇矣。然祉则混举壬戌之狱。以臣祖为诪张矣。 圣教严正。不可以欺。则命祯。就其中拈出翊戴一事。以为荧惑搆诬之计矣。然其所言不过一袭持谦之言而已。今臣欲为条辨。亦不过更申前言。辞说已陈。曲折易眩。谨就前后 圣教及当世先辈儒贤言语文字之所已著见于史乘耳目者。仍及持谦所自言者以證之。其支辞蔓语。率皆略之。以俟 天日之自照焉。癸亥五月十五日疏决时。持谦请仍臣祖门黜。则右议政金锡胄有曰。盖于昨年投书场屋之后。或虑有某㨾危疑之端。果行讥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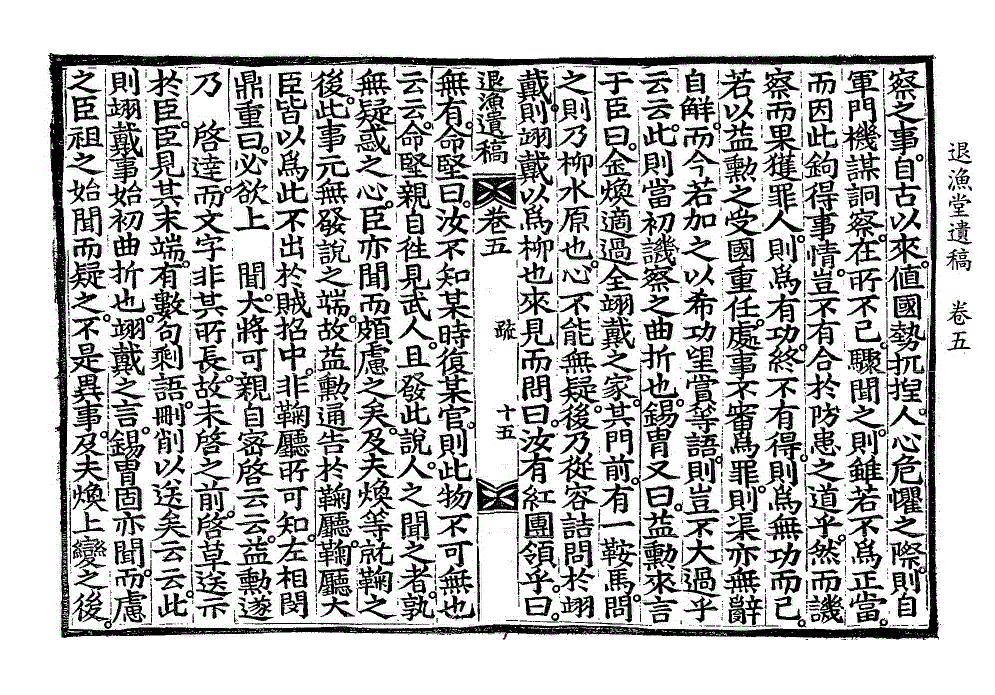 察之事。自古以来。值国势扤捏。人心危惧之际。则自军门机谋诇察。在所不已。骤闻之。则虽若不为正当。而因此钩得事情。岂不有合于防患之道乎。然而讥察而果获罪人。则为有功。终不有得。则为无功而已。若以益勋之受国重任。处事不审为罪。则渠亦无辞自解。而今若加之以希功望赏等语。则岂不大过乎云云。此则当初讥察之曲折也。锡胄又曰。益勋来言于臣曰。金焕适过全翊戴之家。其门前。有一鞍马。问之则乃柳水原也。心不能无疑。后乃从容诘问于翊戴。则翊戴以为柳也来见而问曰。汝有红团领乎。曰。无有。命坚曰。汝不知某时复某官。则此物不可无也云云。命坚亲自往见武人。且发此说。人之闻之者。孰无疑惑之心。臣亦闻而颇虑之矣。及夫焕等就鞠之后。此事元无发说之端。故益勋通告于鞠厅。鞠厅大臣皆以为此不出于贼招中。非鞠厅所可知。左相闵鼎重曰。必欲上 闻。大将可亲自密启云云。益勋遂乃 启达。而文字非其所长。故未启之前。启草送示于臣。臣见其末端。有数句剩语。删削以送矣云云。此则翊戴事始初曲折也。翊戴之言。锡胄固亦闻。而虑之臣祖之始闻而疑之。不是异事。及夫焕上变之后。
察之事。自古以来。值国势扤捏。人心危惧之际。则自军门机谋诇察。在所不已。骤闻之。则虽若不为正当。而因此钩得事情。岂不有合于防患之道乎。然而讥察而果获罪人。则为有功。终不有得。则为无功而已。若以益勋之受国重任。处事不审为罪。则渠亦无辞自解。而今若加之以希功望赏等语。则岂不大过乎云云。此则当初讥察之曲折也。锡胄又曰。益勋来言于臣曰。金焕适过全翊戴之家。其门前。有一鞍马。问之则乃柳水原也。心不能无疑。后乃从容诘问于翊戴。则翊戴以为柳也来见而问曰。汝有红团领乎。曰。无有。命坚曰。汝不知某时复某官。则此物不可无也云云。命坚亲自往见武人。且发此说。人之闻之者。孰无疑惑之心。臣亦闻而颇虑之矣。及夫焕等就鞠之后。此事元无发说之端。故益勋通告于鞠厅。鞠厅大臣皆以为此不出于贼招中。非鞠厅所可知。左相闵鼎重曰。必欲上 闻。大将可亲自密启云云。益勋遂乃 启达。而文字非其所长。故未启之前。启草送示于臣。臣见其末端。有数句剩语。删削以送矣云云。此则翊戴事始初曲折也。翊戴之言。锡胄固亦闻。而虑之臣祖之始闻而疑之。不是异事。及夫焕上变之后。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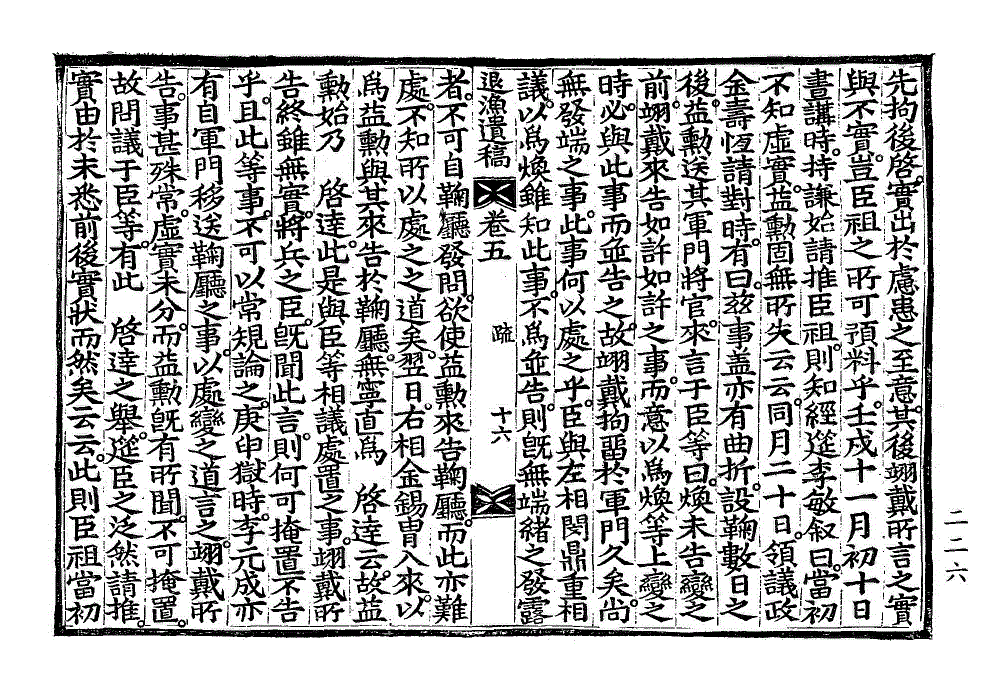 先拘后启。实出于虑患之至意。其后翊戴所言之实与不实。岂臣祖之所可预料乎。壬戌十一月初十日昼讲时。持谦始请推臣祖。则知经筵李敏叙曰。当初不知虚实。益勋固无所失云云。同月二十日。领议政金寿恒请对时。有曰。玆事盖亦有曲折。设鞠数日之后。益勋送其军门将官。来言于臣等曰。焕未告变之前。翊戴来告如许如许之事。而意以为焕等上变之时。必与此事而并告之。故翊戴拘留于军门久矣。尚无发端之事。此事何以处之乎。臣与左相闵鼎重相议。以为焕虽知此事。不为并告。则既无端绪之发露者。不可自鞠厅发问。欲使益勋来告鞠厅。而此亦难处。不知所以处之之道矣。翌日。右相金锡胄入来。以为益勋与其来告于鞠厅。无宁直为 启达云。故益勋始乃 启达。此是与臣等相议处置之事。翊戴所告终虽无实。将兵之臣。既闻此言。则何可掩置不告乎。且此等事。不可以常规论之。庚申狱时。李元成亦有自军门移送鞠厅之事。以处变之道言之。翊戴所告。事甚殊常。虚实未分。而益勋既有所闻。不可掩置。故问议于臣等。有此 启达之举。筵臣之泛然请推。实由于未悉前后实状而然矣云云。此则臣祖当初
先拘后启。实出于虑患之至意。其后翊戴所言之实与不实。岂臣祖之所可预料乎。壬戌十一月初十日昼讲时。持谦始请推臣祖。则知经筵李敏叙曰。当初不知虚实。益勋固无所失云云。同月二十日。领议政金寿恒请对时。有曰。玆事盖亦有曲折。设鞠数日之后。益勋送其军门将官。来言于臣等曰。焕未告变之前。翊戴来告如许如许之事。而意以为焕等上变之时。必与此事而并告之。故翊戴拘留于军门久矣。尚无发端之事。此事何以处之乎。臣与左相闵鼎重相议。以为焕虽知此事。不为并告。则既无端绪之发露者。不可自鞠厅发问。欲使益勋来告鞠厅。而此亦难处。不知所以处之之道矣。翌日。右相金锡胄入来。以为益勋与其来告于鞠厅。无宁直为 启达云。故益勋始乃 启达。此是与臣等相议处置之事。翊戴所告终虽无实。将兵之臣。既闻此言。则何可掩置不告乎。且此等事。不可以常规论之。庚申狱时。李元成亦有自军门移送鞠厅之事。以处变之道言之。翊戴所告。事甚殊常。虚实未分。而益勋既有所闻。不可掩置。故问议于臣等。有此 启达之举。筵臣之泛然请推。实由于未悉前后实状而然矣云云。此则臣祖当初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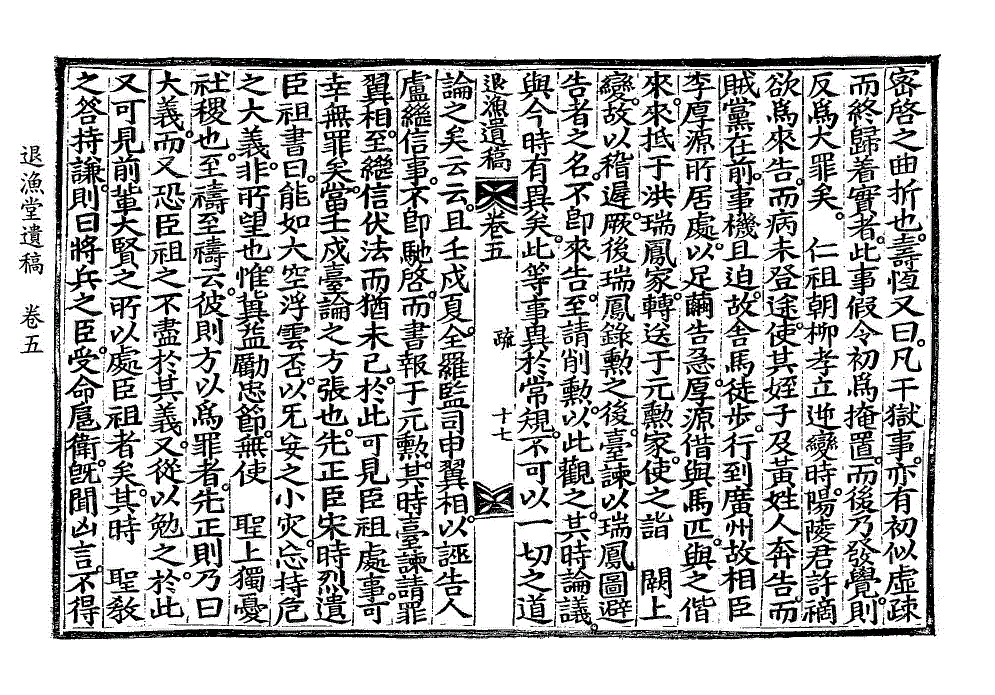 密启之曲折也。寿恒又曰。凡干狱事。亦有初似虚疏而终归着实者。此事假令初为掩置。而后乃发觉。则反为大罪矣。 仁祖朝柳孝立逆变时。阳陵君许𥛚欲为来告。而病未登途。使其侄子及黄姓人奔告。而贼党在前。事机且迫。故舍马徒步。行到广州故相臣李厚源所居处。以足茧告急。厚源借与马匹。与之偕来。来抵于洪瑞凤家。转送于元勋家。使之诣 阙上变。故以稽迟。厥后瑞凤录勋之后。台谏以瑞凤图避告者之名。不即来告。至请削勋。以此观之。其时论议。与今时有异矣。此等事异于常规。不可以一切之道论之矣云云。且壬戌夏。全罗监司申翼相。以诬告人卢继信事。不即驰启。而书报于元勋。其时台谏请罪翼相。至继信伏法而犹未已。于此可见臣祖处事。可幸无罪矣。当壬戌台论之方张也。先正臣宋时烈遗臣祖书曰。能如大空浮云否。以无妄之小灾。忘持危之大义。非所望也。惟冀益励忠节。无使 圣上独忧社稷也。至祷至祷云。彼则方以为罪者。先正则乃曰大义。而又恐臣祖之不尽于其义。又从以勉之。于此又可见前辈大贤之所以处臣祖者矣。其时 圣教之答持谦。则曰将兵之臣。受命扈卫。既闻凶言。不得
密启之曲折也。寿恒又曰。凡干狱事。亦有初似虚疏而终归着实者。此事假令初为掩置。而后乃发觉。则反为大罪矣。 仁祖朝柳孝立逆变时。阳陵君许𥛚欲为来告。而病未登途。使其侄子及黄姓人奔告。而贼党在前。事机且迫。故舍马徒步。行到广州故相臣李厚源所居处。以足茧告急。厚源借与马匹。与之偕来。来抵于洪瑞凤家。转送于元勋家。使之诣 阙上变。故以稽迟。厥后瑞凤录勋之后。台谏以瑞凤图避告者之名。不即来告。至请削勋。以此观之。其时论议。与今时有异矣。此等事异于常规。不可以一切之道论之矣云云。且壬戌夏。全罗监司申翼相。以诬告人卢继信事。不即驰启。而书报于元勋。其时台谏请罪翼相。至继信伏法而犹未已。于此可见臣祖处事。可幸无罪矣。当壬戌台论之方张也。先正臣宋时烈遗臣祖书曰。能如大空浮云否。以无妄之小灾。忘持危之大义。非所望也。惟冀益励忠节。无使 圣上独忧社稷也。至祷至祷云。彼则方以为罪者。先正则乃曰大义。而又恐臣祖之不尽于其义。又从以勉之。于此又可见前辈大贤之所以处臣祖者矣。其时 圣教之答持谦。则曰将兵之臣。受命扈卫。既闻凶言。不得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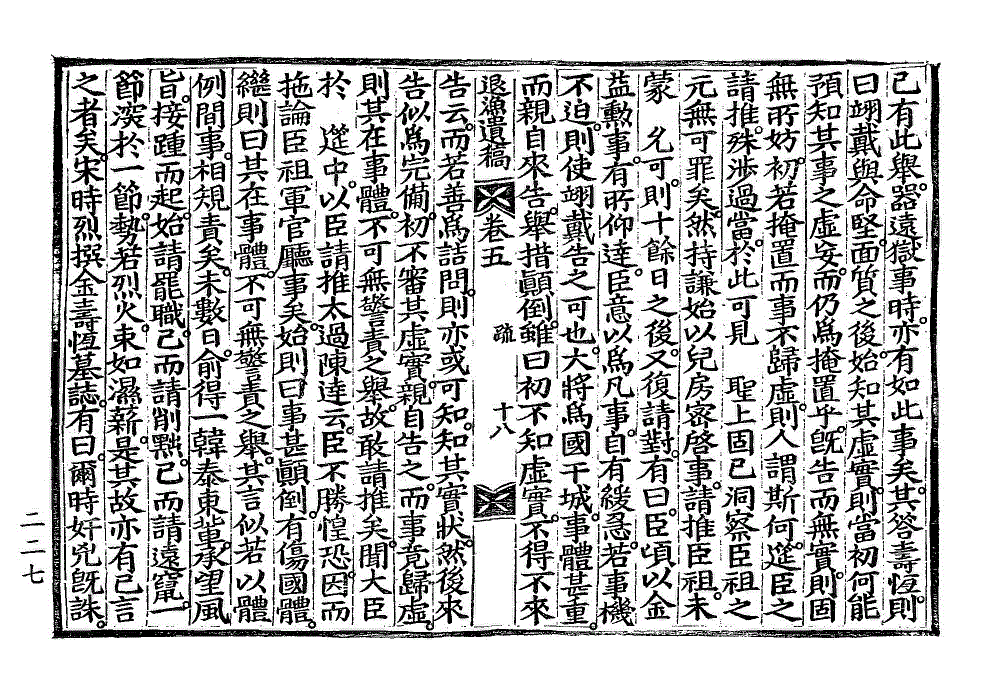 已有此举。器远狱事时。亦有如此事矣。其答寿恒。则曰翊戴与命坚。面质之后。始知其虚实。则当初何能预知其事之虚妄。而仍为掩置乎。既告而无实。则固无所妨。初若掩置而事不归虚。则人谓斯何。筵臣之请推。殊涉过当。于此可见 圣上固已洞察臣祖之元无可罪矣。然持谦始以儿房密启事。请推臣祖。未蒙 允可。则十馀日之后。又复请对。有曰。臣顷以金益勋事。有所仰达。臣意以为凡事。自有缓急。若事机不迫。则使翊戴告之可也。大将为国干城。事体甚重。而亲自来告。举措颠倒。虽曰初不知虚实。不得不来告云。而若善为诘问。则亦或可知。知其实状。然后来告似为完备。初不审其虚实。亲自告之。而事竟归虚。则其在事体。不可无警责之举。故敢请推矣。闻大臣于 筵中。以臣请推太过陈达云。臣不胜惶恐。因而拖论臣祖军官厅事矣。始则曰事甚颠倒。有伤国体。继则曰其在事体。不可无警责之举。其言似若以体例间事。相规责矣。未数日。俞得一韩泰东辈。承望风旨。接踵而起。始请罢职。已而请削黜。已而请远窜。一节深于一节。势若烈火。束如湿薪。是其故亦有已言之者矣。宋时烈撰金寿恒墓志。有曰。尔时奸凶既诛。
已有此举。器远狱事时。亦有如此事矣。其答寿恒。则曰翊戴与命坚。面质之后。始知其虚实。则当初何能预知其事之虚妄。而仍为掩置乎。既告而无实。则固无所妨。初若掩置而事不归虚。则人谓斯何。筵臣之请推。殊涉过当。于此可见 圣上固已洞察臣祖之元无可罪矣。然持谦始以儿房密启事。请推臣祖。未蒙 允可。则十馀日之后。又复请对。有曰。臣顷以金益勋事。有所仰达。臣意以为凡事。自有缓急。若事机不迫。则使翊戴告之可也。大将为国干城。事体甚重。而亲自来告。举措颠倒。虽曰初不知虚实。不得不来告云。而若善为诘问。则亦或可知。知其实状。然后来告似为完备。初不审其虚实。亲自告之。而事竟归虚。则其在事体。不可无警责之举。故敢请推矣。闻大臣于 筵中。以臣请推太过陈达云。臣不胜惶恐。因而拖论臣祖军官厅事矣。始则曰事甚颠倒。有伤国体。继则曰其在事体。不可无警责之举。其言似若以体例间事。相规责矣。未数日。俞得一韩泰东辈。承望风旨。接踵而起。始请罢职。已而请削黜。已而请远窜。一节深于一节。势若烈火。束如湿薪。是其故亦有已言之者矣。宋时烈撰金寿恒墓志。有曰。尔时奸凶既诛。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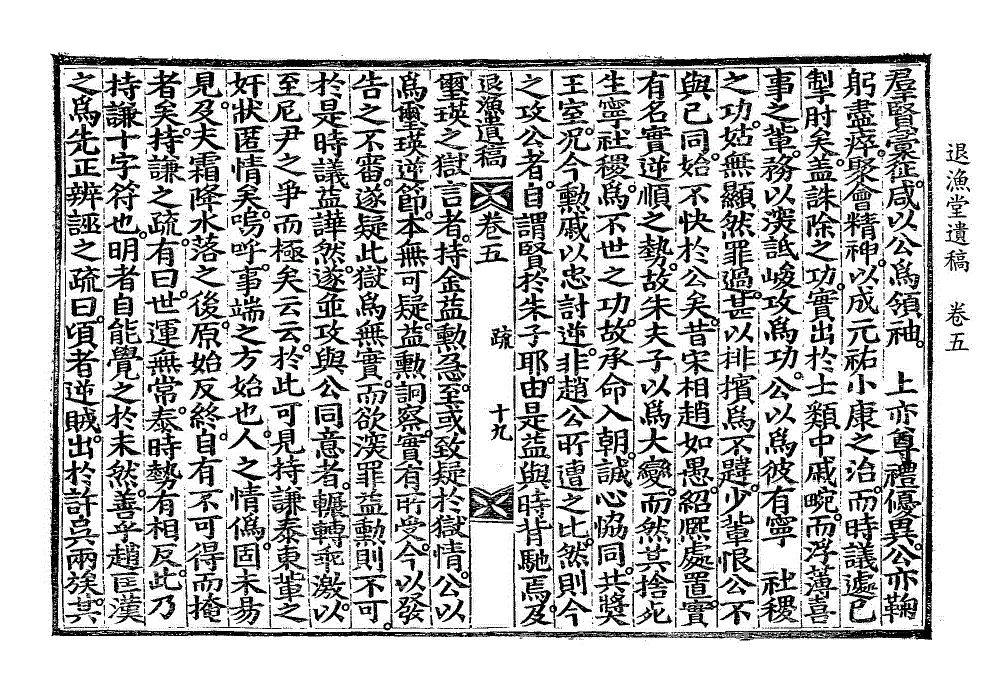 群贤汇征。咸以公为领袖。 上亦尊礼优异。公亦鞠躬尽瘁。聚会精神。以成元祐小康之治。而时议遽已掣肘矣。盖诛除之功。实出于士类中戚畹。而浮薄喜事之辈。务以深诋峻攻为功。公以为彼有宁 社稷之功。姑无显然罪过。甚以排摈为不韪。少辈恨公不与己同。始不快于公矣。昔宋相赵如愚。绍熙处置。实有名实逆顺之势。故朱夫子以为大变。而然其舍死生宁社稷。为不世之功。故承命入朝。诚心协同。共奖王室。况今勋戚以忠讨逆。非赵公所遭之比。然则今之攻公者。自谓贤于朱子耶。由是益与时背驰焉。及玺瑛之狱言者。持金益勋急。至或致疑于狱情。公以为玺瑛逆节。本无可疑。益勋诇察。实有所受。今以发告之不审。遂疑此狱为无实。而欲深罪益勋则不可。于是时议益哗然。遂并攻与公同意者。辗转乖激。以至尼尹之争而极矣云云。于此可见持谦泰东辈之奸状匿情矣。呜呼。事端之方始也。人之情伪。固未易见。及夫霜降水落之后。原始反终。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持谦之疏。有曰。世运无常。泰时势有相反。此乃持谦十字符也。明者自能觉之于未然。善乎赵匡汉之为先正辨诬之疏曰。顷者逆贼。出于许,吴两族。其
群贤汇征。咸以公为领袖。 上亦尊礼优异。公亦鞠躬尽瘁。聚会精神。以成元祐小康之治。而时议遽已掣肘矣。盖诛除之功。实出于士类中戚畹。而浮薄喜事之辈。务以深诋峻攻为功。公以为彼有宁 社稷之功。姑无显然罪过。甚以排摈为不韪。少辈恨公不与己同。始不快于公矣。昔宋相赵如愚。绍熙处置。实有名实逆顺之势。故朱夫子以为大变。而然其舍死生宁社稷。为不世之功。故承命入朝。诚心协同。共奖王室。况今勋戚以忠讨逆。非赵公所遭之比。然则今之攻公者。自谓贤于朱子耶。由是益与时背驰焉。及玺瑛之狱言者。持金益勋急。至或致疑于狱情。公以为玺瑛逆节。本无可疑。益勋诇察。实有所受。今以发告之不审。遂疑此狱为无实。而欲深罪益勋则不可。于是时议益哗然。遂并攻与公同意者。辗转乖激。以至尼尹之争而极矣云云。于此可见持谦泰东辈之奸状匿情矣。呜呼。事端之方始也。人之情伪。固未易见。及夫霜降水落之后。原始反终。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持谦之疏。有曰。世运无常。泰时势有相反。此乃持谦十字符也。明者自能觉之于未然。善乎赵匡汉之为先正辨诬之疏曰。顷者逆贼。出于许,吴两族。其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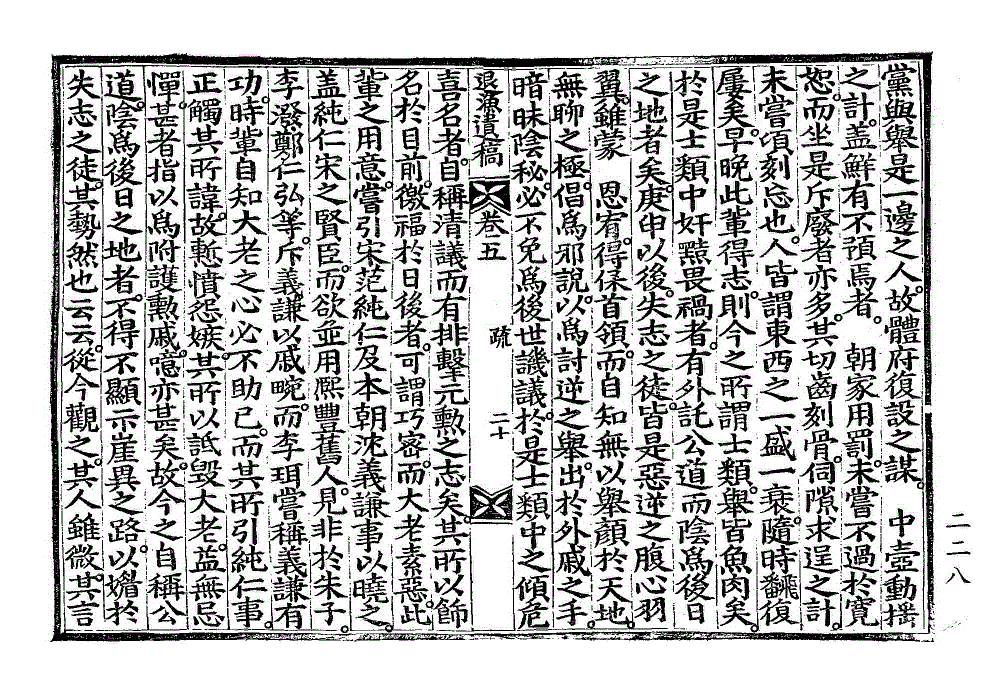 党与举是一边之人。故体府复设之谋。 中壸动摇之计。盖鲜有不预焉者。 朝家用罚。未尝不过于宽恕。而坐是斥废者亦多。其切齿刻骨。伺隙求逞之计。未尝顷刻忘也。人皆谓东西之一盛一衰。随时翻复屡矣。早晚此辈得志。则今之所谓士类。举皆鱼肉矣。于是士类中奸黠畏祸者。有外托公道而阴为后日之地者矣。庚申以后。失志之徒。皆是恶逆之腹心羽翼。虽蒙 恩宥。得保首领。而自知无以举颜于天地。无聊之极。倡为邪说。以为讨逆之举。出于外戚之手。暗昧阴秘。必不免为后世讥议。于是士类中之倾危喜名者。自称清议而有排击元勋之志矣。其所以饰名于目前。徼福于日后者。可谓巧密。而大老素恶。此辈之用意。尝引宋范纯仁及本朝沈义谦事以晓之。盖纯仁宋之贤臣。而欲并用熙丰旧人。见非于朱子。李泼,郑仁弘等。斥义谦以戚畹。而李珥尝称义谦有功。时辈自知大老之心必不助己。而其所引纯仁事。正触其所讳。故惭愤怨嫉。其所以诋毁大老。益无忌惮。甚者指以为附护勋戚。噫亦甚矣。故今之自称公道。阴为后日之地者。不得不显示崖异之路。以媚于失志之徒。其势然也云云。从今观之。其人虽微。其言
党与举是一边之人。故体府复设之谋。 中壸动摇之计。盖鲜有不预焉者。 朝家用罚。未尝不过于宽恕。而坐是斥废者亦多。其切齿刻骨。伺隙求逞之计。未尝顷刻忘也。人皆谓东西之一盛一衰。随时翻复屡矣。早晚此辈得志。则今之所谓士类。举皆鱼肉矣。于是士类中奸黠畏祸者。有外托公道而阴为后日之地者矣。庚申以后。失志之徒。皆是恶逆之腹心羽翼。虽蒙 恩宥。得保首领。而自知无以举颜于天地。无聊之极。倡为邪说。以为讨逆之举。出于外戚之手。暗昧阴秘。必不免为后世讥议。于是士类中之倾危喜名者。自称清议而有排击元勋之志矣。其所以饰名于目前。徼福于日后者。可谓巧密。而大老素恶。此辈之用意。尝引宋范纯仁及本朝沈义谦事以晓之。盖纯仁宋之贤臣。而欲并用熙丰旧人。见非于朱子。李泼,郑仁弘等。斥义谦以戚畹。而李珥尝称义谦有功。时辈自知大老之心必不助己。而其所引纯仁事。正触其所讳。故惭愤怨嫉。其所以诋毁大老。益无忌惮。甚者指以为附护勋戚。噫亦甚矣。故今之自称公道。阴为后日之地者。不得不显示崖异之路。以媚于失志之徒。其势然也云云。从今观之。其人虽微。其言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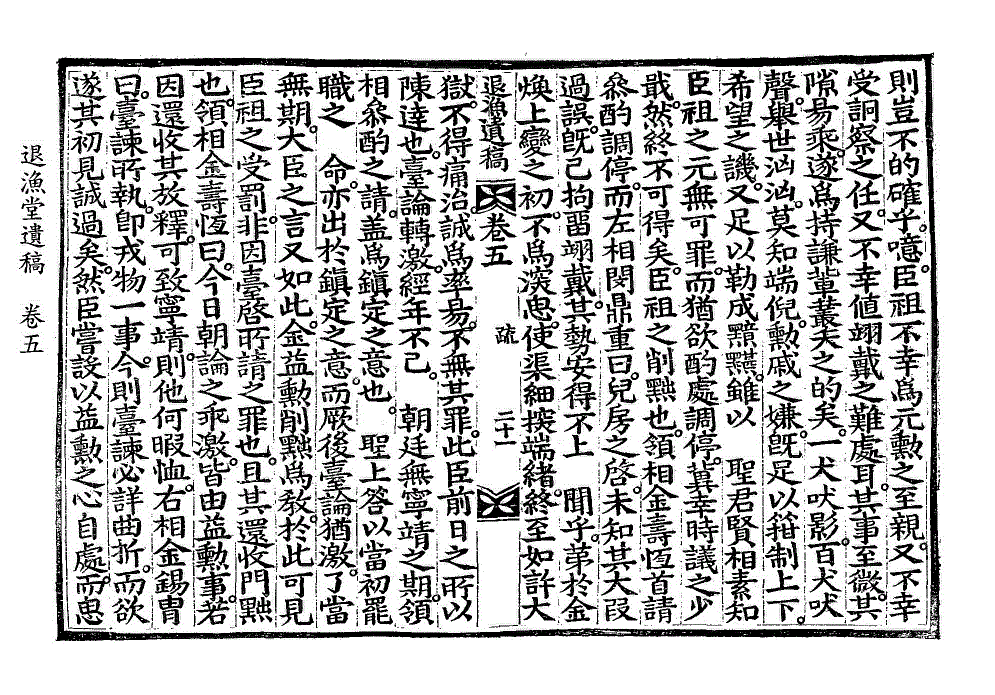 则岂不的确乎。噫。臣祖不幸为元勋之至亲。又不幸受诇察之任。又不幸值翊戴之难处耳。其事至微。其隙易乘。遂为持谦辈丛矢之的矣。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举世汹汹。莫知端倪。勋戚之嫌。既足以钳制上下。希望之讥。又足以勒成黯黮。虽以 圣君贤相素知臣祖之元无可罪。而犹欲酌处调停。冀幸时议之少戢。然终不可得矣。臣祖之削黜也。领相金寿恒首请参酌调停。而左相闵鼎重曰。儿房之启。未知其大段过误。既已拘留翊戴。其势安得不上 闻乎。第于金焕上变之初。不为深思。使渠细探端绪。终至如许大狱。不得痛治。诚为率易。不无其罪。此臣前日之所以陈达也。台论转激。经年不已。 朝廷无宁靖之期。领相参酌之请。盖为镇定之意也。 圣上答以当初罢职之 命。亦出于镇定之意。而厥后台论犹激。了当无期。大臣之言又如此。金益勋削黜为教。于此可见臣祖之受罚。非因台启所请之罪也。且其还收门黜也。领相金寿恒曰。今日朝论之乖激。皆由益勋事。若因还收其放释。可致宁靖。则他何暇恤。右相金锡胄曰。台谏所执。即戎物一事。今则台谏必详曲折。而欲遂其初见诚过矣。然臣尝设以益勋之心自处。而思
则岂不的确乎。噫。臣祖不幸为元勋之至亲。又不幸受诇察之任。又不幸值翊戴之难处耳。其事至微。其隙易乘。遂为持谦辈丛矢之的矣。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举世汹汹。莫知端倪。勋戚之嫌。既足以钳制上下。希望之讥。又足以勒成黯黮。虽以 圣君贤相素知臣祖之元无可罪。而犹欲酌处调停。冀幸时议之少戢。然终不可得矣。臣祖之削黜也。领相金寿恒首请参酌调停。而左相闵鼎重曰。儿房之启。未知其大段过误。既已拘留翊戴。其势安得不上 闻乎。第于金焕上变之初。不为深思。使渠细探端绪。终至如许大狱。不得痛治。诚为率易。不无其罪。此臣前日之所以陈达也。台论转激。经年不已。 朝廷无宁靖之期。领相参酌之请。盖为镇定之意也。 圣上答以当初罢职之 命。亦出于镇定之意。而厥后台论犹激。了当无期。大臣之言又如此。金益勋削黜为教。于此可见臣祖之受罚。非因台启所请之罪也。且其还收门黜也。领相金寿恒曰。今日朝论之乖激。皆由益勋事。若因还收其放释。可致宁靖。则他何暇恤。右相金锡胄曰。台谏所执。即戎物一事。今则台谏必详曲折。而欲遂其初见诚过矣。然臣尝设以益勋之心自处。而思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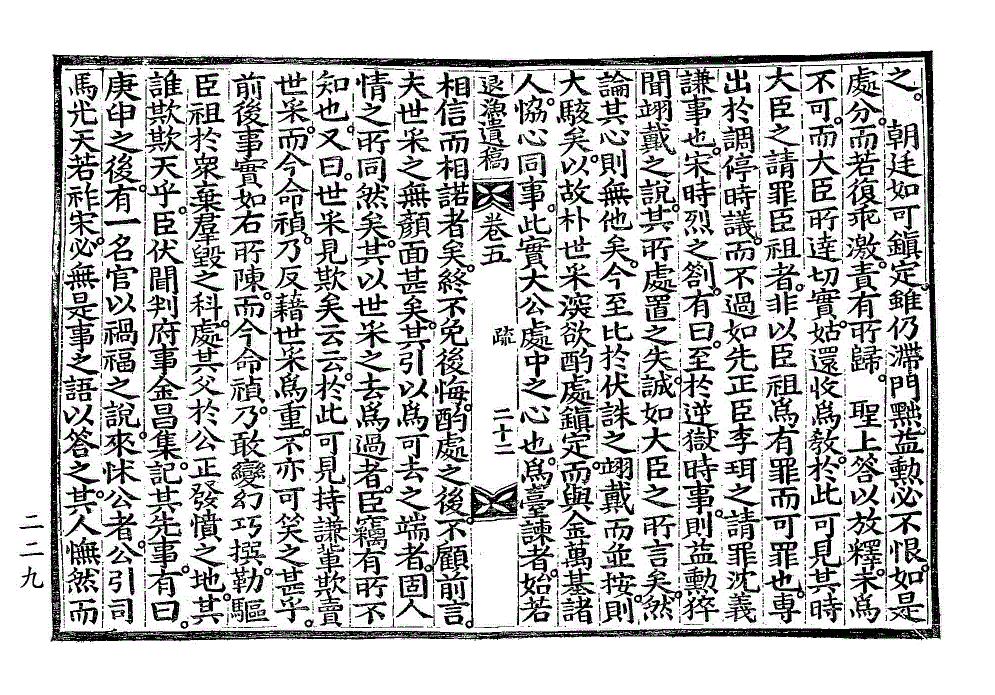 之。 朝廷如可镇定。虽仍滞门黜。益勋必不恨。如是处分。而若复乖激。责有所归。 圣上答以放释。未为不可。而大臣所达切实。姑还收为教。于此可见其时大臣之请罪臣祖者。非以臣祖为有罪而可罪也。专出于调停时议。而不过如先正臣李珥之请罪沈义谦事也。宋时烈之劄。有曰。至于逆狱时事。则益勋猝闻翊戴之说。其所处置之失。诚如大臣之所言矣。然论其心则无他矣。今至比于伏诛之翊戴而并按。则大骇矣。以故朴世采深欲酌处镇定。而与金万基诸人。协心同事。此实大公处中之心也。为台谏者。始若相信而相诺者矣。终不免后悔。酌处之后。不顾前言。夫世采之无颜面甚矣。其引以为可去之端者。固人情之所同然矣。其以世采之去为过者。臣窃有所不知也。又曰。世采见欺矣云云。于此可见持谦辈欺卖世采。而今命祯。乃反藉世采为重。不亦可笑之甚乎。前后事实如右所陈。而今命祯。乃敢变幻巧撰。勒驱臣祖于众弃群毁之科。处其父于公正发愤之地。其谁欺欺天乎。臣伏闻判府事金昌集。记其先事。有曰。庚申之后。有一名官以祸福之说。来怵公者。公引司马光天若祚宋。必无是事之语以答之。其人怃然而
之。 朝廷如可镇定。虽仍滞门黜。益勋必不恨。如是处分。而若复乖激。责有所归。 圣上答以放释。未为不可。而大臣所达切实。姑还收为教。于此可见其时大臣之请罪臣祖者。非以臣祖为有罪而可罪也。专出于调停时议。而不过如先正臣李珥之请罪沈义谦事也。宋时烈之劄。有曰。至于逆狱时事。则益勋猝闻翊戴之说。其所处置之失。诚如大臣之所言矣。然论其心则无他矣。今至比于伏诛之翊戴而并按。则大骇矣。以故朴世采深欲酌处镇定。而与金万基诸人。协心同事。此实大公处中之心也。为台谏者。始若相信而相诺者矣。终不免后悔。酌处之后。不顾前言。夫世采之无颜面甚矣。其引以为可去之端者。固人情之所同然矣。其以世采之去为过者。臣窃有所不知也。又曰。世采见欺矣云云。于此可见持谦辈欺卖世采。而今命祯。乃反藉世采为重。不亦可笑之甚乎。前后事实如右所陈。而今命祯。乃敢变幻巧撰。勒驱臣祖于众弃群毁之科。处其父于公正发愤之地。其谁欺欺天乎。臣伏闻判府事金昌集。记其先事。有曰。庚申之后。有一名官以祸福之说。来怵公者。公引司马光天若祚宋。必无是事之语以答之。其人怃然而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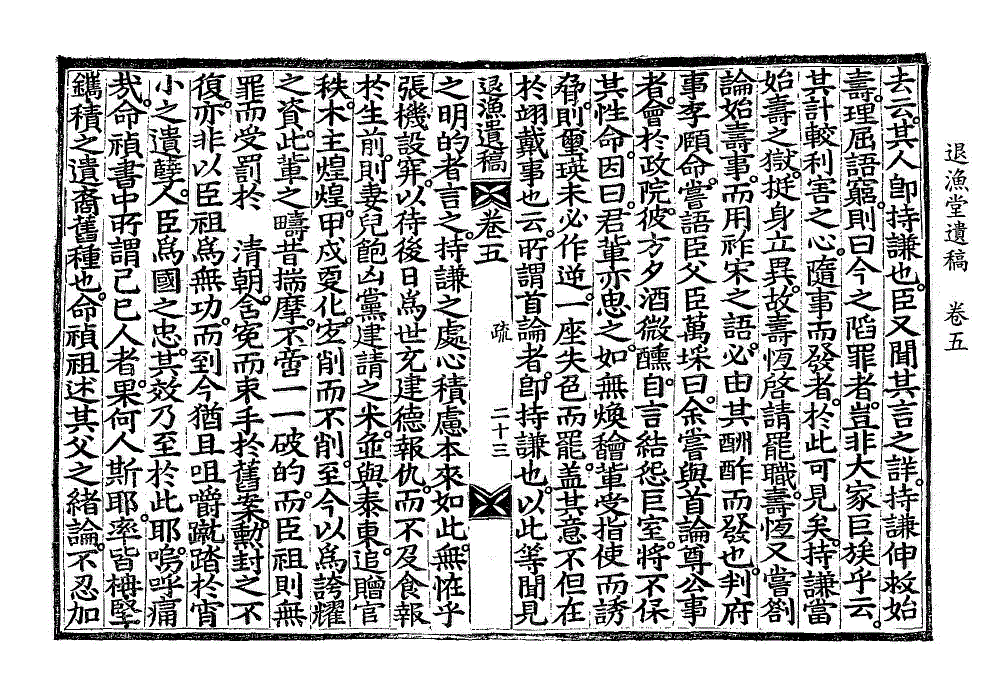 去云。其人即持谦也。臣又闻其言之详。持谦伸救始寿。理屈语穷。则曰今之陷罪者。岂非大家巨族乎云。其计较利害之心。随事而发者。于此可见矣。持谦当始寿之狱。挺身立异。故寿恒启请罢职。寿恒又尝劄论始寿事。而用祚宋之语。必由其酬酢而发也。判府事李颐命。尝语臣父臣万埰曰。余尝与首论尊公事者。会于政院。彼方夕酒微醺。自言结怨巨室。将不保其性命。因曰。君辈亦思之。如无焕
去云。其人即持谦也。臣又闻其言之详。持谦伸救始寿。理屈语穷。则曰今之陷罪者。岂非大家巨族乎云。其计较利害之心。随事而发者。于此可见矣。持谦当始寿之狱。挺身立异。故寿恒启请罢职。寿恒又尝劄论始寿事。而用祚宋之语。必由其酬酢而发也。判府事李颐命。尝语臣父臣万埰曰。余尝与首论尊公事者。会于政院。彼方夕酒微醺。自言结怨巨室。将不保其性命。因曰。君辈亦思之。如无焕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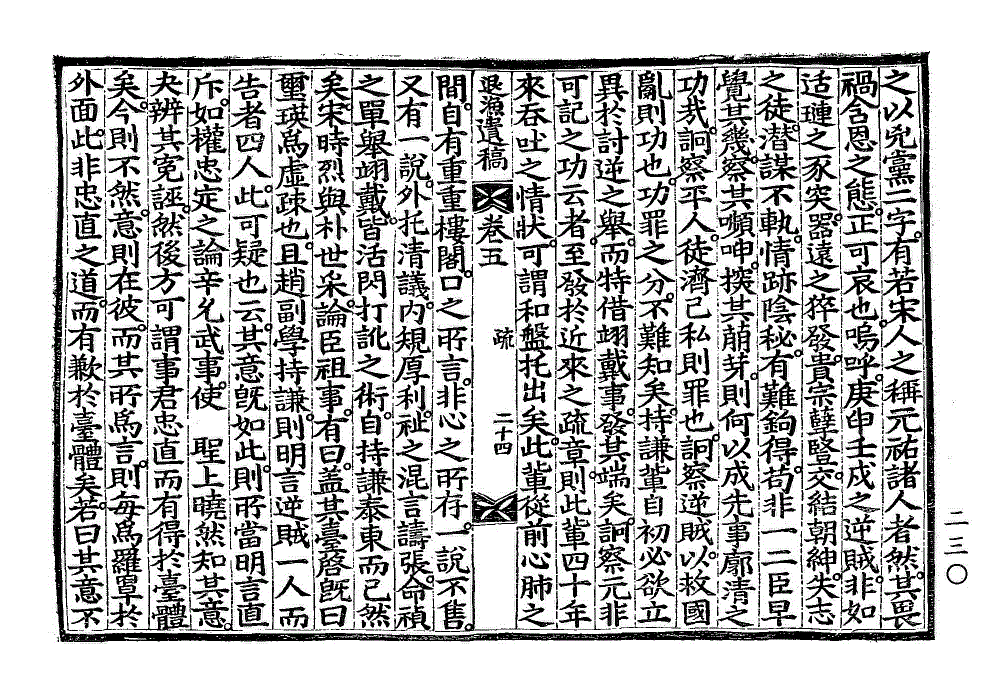 之以凶党二字。有若宋人之称元祐诸人者然。其畏祸含恩之态。正可哀也。呜呼。庚申壬戌之逆贼。非如适琏之豕突。器远之猝发。贵宗孽竖。交结朝绅。失志之徒。潜谋不轨。情迹阴秘。有难钩得。苟非一二臣早觉其几。察其嚬呻。探其萌芽。则何以成先事廓清之功哉。诇察平人。徒济己私则罪也。诇察逆贼。以救国乱则功也。功罪之分。不难知矣。持谦辈自初必欲立异于讨逆之举。而特借翊戴事。发其端矣。诇察元非可记之功云者。至发于近来之疏章。则此辈四十年来吞吐之情状。可谓和盘托出矣。此辈从前心肺之间。自有重重楼阁。口之所言。非心之所存。一说不售。又有一说。外托清议。内规厚利。祉之混言诪张。命祯之单举翊戴。皆活闪打讹之术。自持谦泰东而已然矣。宋时烈与朴世采。论臣祖事。有曰。盖其台启既曰玺瑛为虚疏也。且赵副学持谦。则明言逆贼一人而告者四人。此可疑也云。其意既如此。则所当明言直斥。如权忠定之论辛允武事。使 圣上晓然知其意。夬辨其冤诬。然后方可谓事君忠直而有得于台体矣。今则不然。意则在彼。而其所为言。则每为罗罩于外面。此非忠直之道。而有歉于台体矣。若曰其意不
之以凶党二字。有若宋人之称元祐诸人者然。其畏祸含恩之态。正可哀也。呜呼。庚申壬戌之逆贼。非如适琏之豕突。器远之猝发。贵宗孽竖。交结朝绅。失志之徒。潜谋不轨。情迹阴秘。有难钩得。苟非一二臣早觉其几。察其嚬呻。探其萌芽。则何以成先事廓清之功哉。诇察平人。徒济己私则罪也。诇察逆贼。以救国乱则功也。功罪之分。不难知矣。持谦辈自初必欲立异于讨逆之举。而特借翊戴事。发其端矣。诇察元非可记之功云者。至发于近来之疏章。则此辈四十年来吞吐之情状。可谓和盘托出矣。此辈从前心肺之间。自有重重楼阁。口之所言。非心之所存。一说不售。又有一说。外托清议。内规厚利。祉之混言诪张。命祯之单举翊戴。皆活闪打讹之术。自持谦泰东而已然矣。宋时烈与朴世采。论臣祖事。有曰。盖其台启既曰玺瑛为虚疏也。且赵副学持谦。则明言逆贼一人而告者四人。此可疑也云。其意既如此。则所当明言直斥。如权忠定之论辛允武事。使 圣上晓然知其意。夬辨其冤诬。然后方可谓事君忠直而有得于台体矣。今则不然。意则在彼。而其所为言。则每为罗罩于外面。此非忠直之道。而有歉于台体矣。若曰其意不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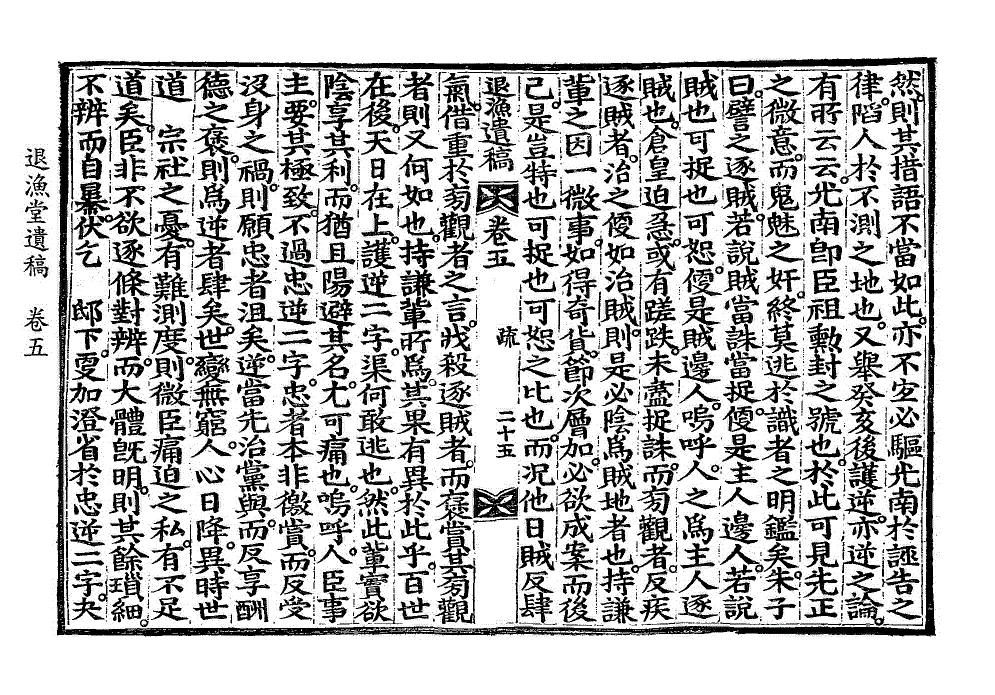 然。则其措语不当如此。亦不宜必驱光南于诬告之律。陷人于不测之地也。又举癸亥后护逆。亦逆之论。有所云云。光南即臣祖勋封之号也。于此可见先正之微意。而鬼魅之奸。终莫逃于识者之明鉴矣。朱子曰。譬之逐贼。若说贼当诛当捉。便是主人边人。若说贼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贼边人。呜呼。人之为主人逐贼也。仓皇迫急。或有蹉跌。未尽捉诛。而旁观者。反疾逐贼者。治之便如治贼。则是必阴为贼地者也。持谦辈之因一微事。如得奇货。节次层加。必欲成案而后已。是岂特也可捉也可恕之比也。而况他日贼反肆气。借重于旁观者之言。戕杀逐贼者。而褒赏其旁观者则又何如也。持谦辈所为。其果有异于此乎。百世在后。天日在上。护逆二字。渠何敢逃也。然此辈实欲阴享其利。而犹且阳避其名。尤可痛也。呜呼。人臣事主。要其极致。不过忠逆二字。忠者本非徼赏。而反受没身之祸。则愿忠者沮矣。逆当先治党与。而反享酬德之褒。则为逆者肆矣。世变无穷。人心日降。异时世道 宗社之忧。有难测度。则微臣痛迫之私。有不足道矣。臣非不欲逐条对辨。而大体既明。则其馀琐细。不辨而自㬥。伏乞 邸下。更加澄省于忠逆二字。夬
然。则其措语不当如此。亦不宜必驱光南于诬告之律。陷人于不测之地也。又举癸亥后护逆。亦逆之论。有所云云。光南即臣祖勋封之号也。于此可见先正之微意。而鬼魅之奸。终莫逃于识者之明鉴矣。朱子曰。譬之逐贼。若说贼当诛当捉。便是主人边人。若说贼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贼边人。呜呼。人之为主人逐贼也。仓皇迫急。或有蹉跌。未尽捉诛。而旁观者。反疾逐贼者。治之便如治贼。则是必阴为贼地者也。持谦辈之因一微事。如得奇货。节次层加。必欲成案而后已。是岂特也可捉也可恕之比也。而况他日贼反肆气。借重于旁观者之言。戕杀逐贼者。而褒赏其旁观者则又何如也。持谦辈所为。其果有异于此乎。百世在后。天日在上。护逆二字。渠何敢逃也。然此辈实欲阴享其利。而犹且阳避其名。尤可痛也。呜呼。人臣事主。要其极致。不过忠逆二字。忠者本非徼赏。而反受没身之祸。则愿忠者沮矣。逆当先治党与。而反享酬德之褒。则为逆者肆矣。世变无穷。人心日降。异时世道 宗社之忧。有难测度。则微臣痛迫之私。有不足道矣。臣非不欲逐条对辨。而大体既明。则其馀琐细。不辨而自㬥。伏乞 邸下。更加澄省于忠逆二字。夬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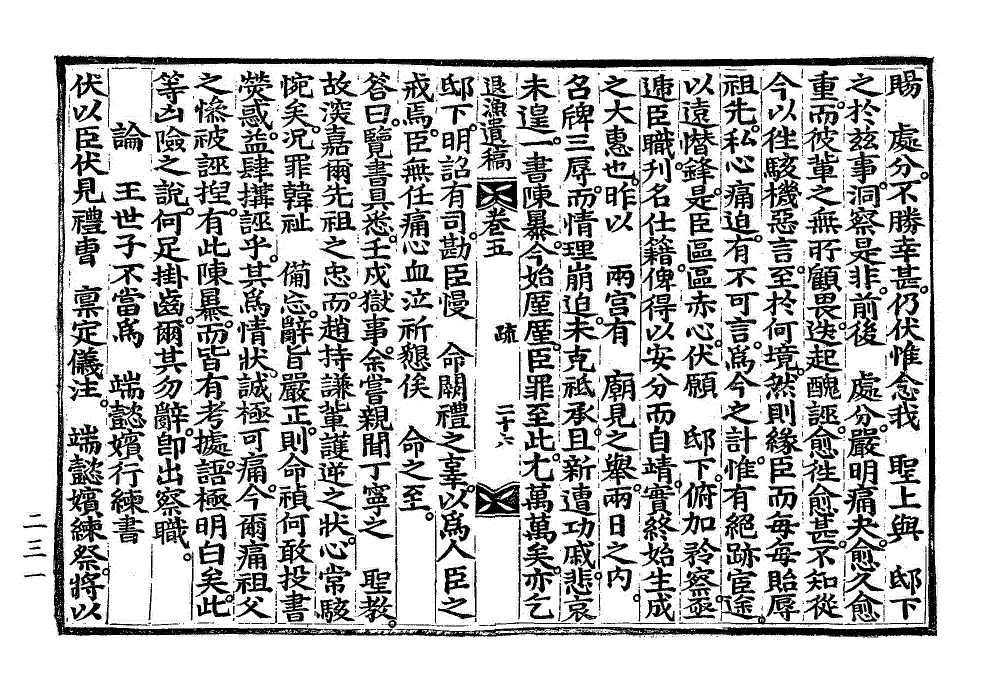 赐 处分。不胜幸甚。仍伏惟念我 圣上与 邸下之于玆事。洞察是非。前后 处分。严明痛夬。愈久愈重。而彼辈之无所顾畏。迭起丑诬。愈往愈甚。不知从今以往骇机恶言。至于何境。然则缘臣而每每贻辱祖先。私心痛迫。有不可言。为今之计。惟有绝迹宦途。以远憯锋。是臣区区赤心。伏愿 邸下。俯加矜察。亟递臣职。刊名仕籍。俾得以安分而自靖。实终始生成之大惠也。昨以 两宫有 庙见之举。两日之内。 召牌三辱。而情理崩迫。未克祗承。且新遭功戚。悲哀未遑。一书陈㬥。今始廑廑。臣罪至此。尤万万矣。亦乞邸下。明诏有司。勘臣慢 命阙礼之辜。以为人臣之戒焉。臣无任痛心血泣祈恳俟 命之至。
赐 处分。不胜幸甚。仍伏惟念我 圣上与 邸下之于玆事。洞察是非。前后 处分。严明痛夬。愈久愈重。而彼辈之无所顾畏。迭起丑诬。愈往愈甚。不知从今以往骇机恶言。至于何境。然则缘臣而每每贻辱祖先。私心痛迫。有不可言。为今之计。惟有绝迹宦途。以远憯锋。是臣区区赤心。伏愿 邸下。俯加矜察。亟递臣职。刊名仕籍。俾得以安分而自靖。实终始生成之大惠也。昨以 两宫有 庙见之举。两日之内。 召牌三辱。而情理崩迫。未克祗承。且新遭功戚。悲哀未遑。一书陈㬥。今始廑廑。臣罪至此。尤万万矣。亦乞邸下。明诏有司。勘臣慢 命阙礼之辜。以为人臣之戒焉。臣无任痛心血泣祈恳俟 命之至。答曰。览书具悉。壬戌狱事。余尝亲闻丁宁之 圣教。故深嘉尔先祖之忠。而赵持谦辈护逆之状。心常骇惋矣。况罪韩祉 备忘。辞旨严正。则命祯何敢投书荧惑。益肆搆诬乎。其为情状。诚极可痛。今尔痛祖父之惨被诬捏。有此陈㬥。而皆有考据。语极明白矣。此等凶险之说。何足挂齿。尔其勿辞。即出察职。
论 王世子不当为 端懿嫔行练书
伏以臣伏见礼曹 禀定仪注。 端懿嫔练祭。将以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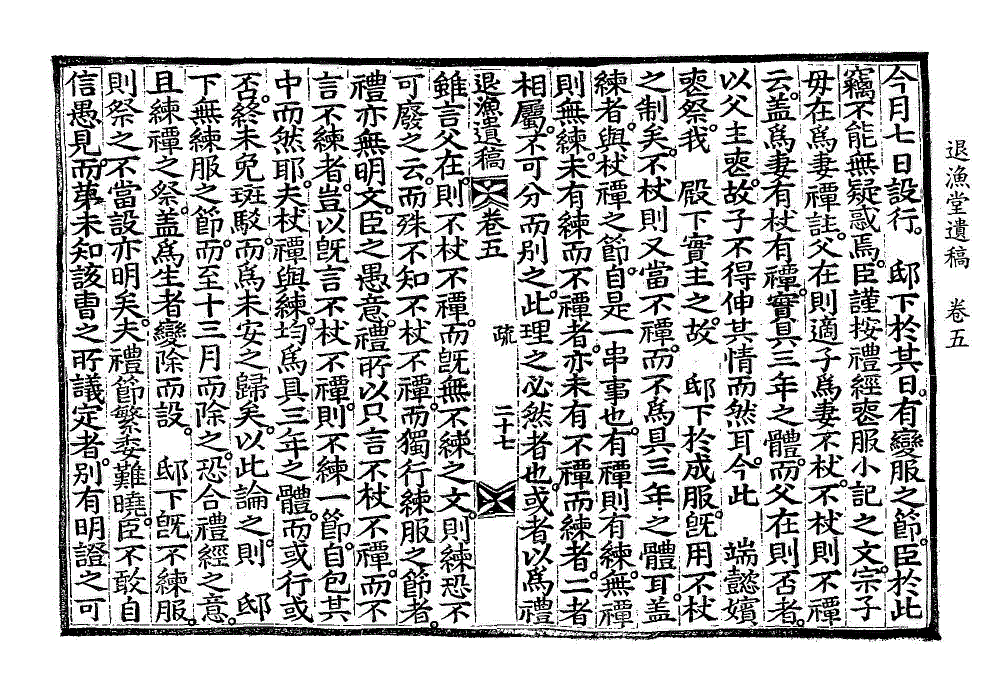 今月七日设行。 邸下于其日。有变服之节。臣于此窃不能无疑惑焉。臣谨按礼经丧服小记之文。宗子母在为妻禫注。父在则适子为妻不杖。不杖则不禫云。盖为妻有杖有禫。实具三年之体。而父在则否者。以父主丧。故子不得伸其情而然耳。今此 端懿嫔丧祭。我 殿下实主之。故 邸下于成服。既用不杖之制矣。不杖则又当不禫。而不为具三年之体耳。盖练者。与杖禫之节。自是一串事也。有禫则有练。无禫则无练。未有练而不禫者。亦未有不禫而练者。二者相属。不可分而别之。此理之必然者也。或者以为礼虽言父在。则不杖不禫。而既无不练之文。则练恐不可废之云。而殊不知不杖不禫。而独行练服之节者。礼亦无明文。臣之愚意。礼所以只言不杖不禫。而不言不练者。岂以既言不杖不禫。则不练一节。自包其中而然耶。夫杖禫与练。均为具三年之体。而或行或否。终未免斑驳。而为未安之归矣。以此论之。则 邸下无练服之节。而至十三月而除之。恐合礼经之意。且练禫之祭。盖为生者变除而设。 邸下既不练服。则祭之不当设亦明矣。夫礼节繁委难晓。臣不敢自信愚见。而第未知该曹之所议定者。别有明證之可
今月七日设行。 邸下于其日。有变服之节。臣于此窃不能无疑惑焉。臣谨按礼经丧服小记之文。宗子母在为妻禫注。父在则适子为妻不杖。不杖则不禫云。盖为妻有杖有禫。实具三年之体。而父在则否者。以父主丧。故子不得伸其情而然耳。今此 端懿嫔丧祭。我 殿下实主之。故 邸下于成服。既用不杖之制矣。不杖则又当不禫。而不为具三年之体耳。盖练者。与杖禫之节。自是一串事也。有禫则有练。无禫则无练。未有练而不禫者。亦未有不禫而练者。二者相属。不可分而别之。此理之必然者也。或者以为礼虽言父在。则不杖不禫。而既无不练之文。则练恐不可废之云。而殊不知不杖不禫。而独行练服之节者。礼亦无明文。臣之愚意。礼所以只言不杖不禫。而不言不练者。岂以既言不杖不禫。则不练一节。自包其中而然耶。夫杖禫与练。均为具三年之体。而或行或否。终未免斑驳。而为未安之归矣。以此论之。则 邸下无练服之节。而至十三月而除之。恐合礼经之意。且练禫之祭。盖为生者变除而设。 邸下既不练服。则祭之不当设亦明矣。夫礼节繁委难晓。臣不敢自信愚见。而第未知该曹之所议定者。别有明證之可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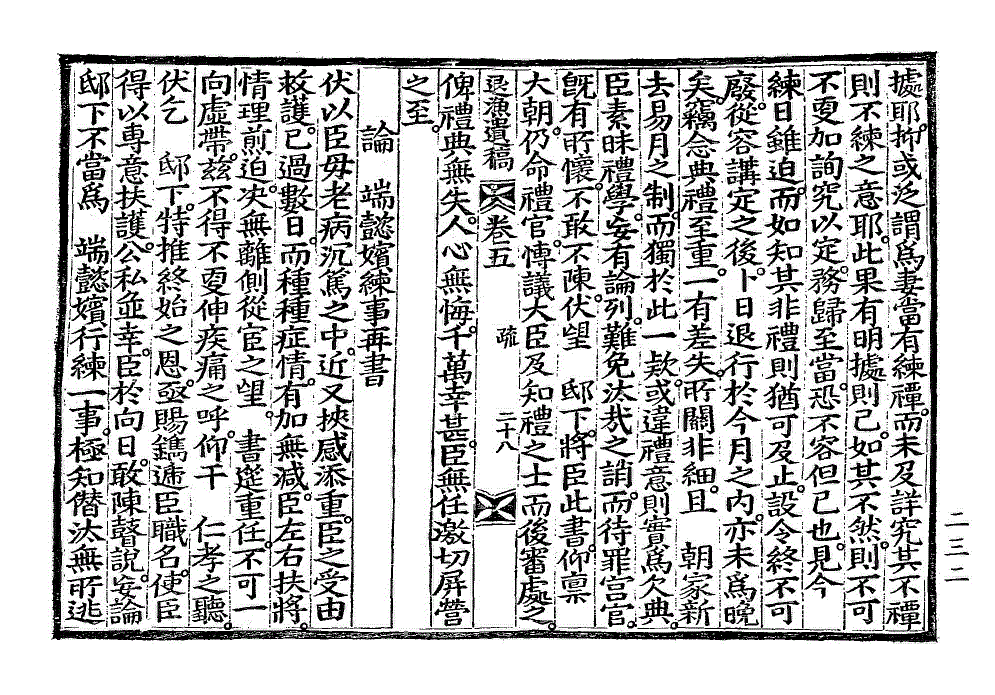 据耶。抑或泛谓为妻当有练禫。而未及详究其不禫则不练之意耶。此果有明据则已。如其不然。则不可不更加询究以定。务归至当。恐不容但已也。见今 练日虽迫。而如知其非礼则犹可及止。设令终不可废。从容讲定之后。卜日退行于今月之内。亦未为晚矣。窃念典礼至重。一有差失。所关非细。且 朝家新去易月之制。而独于此一款。或违礼意则实为欠典。臣素昧礼学。妄有论列。难免汰哉之诮。而待罪宫官。既有所怀。不敢不陈。伏望 邸下。将臣此书。仰禀 大朝。仍命礼官。博议大臣及知礼之士而后审处之。俾礼典无失。人心无悔。千万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据耶。抑或泛谓为妻当有练禫。而未及详究其不禫则不练之意耶。此果有明据则已。如其不然。则不可不更加询究以定。务归至当。恐不容但已也。见今 练日虽迫。而如知其非礼则犹可及止。设令终不可废。从容讲定之后。卜日退行于今月之内。亦未为晚矣。窃念典礼至重。一有差失。所关非细。且 朝家新去易月之制。而独于此一款。或违礼意则实为欠典。臣素昧礼学。妄有论列。难免汰哉之诮。而待罪宫官。既有所怀。不敢不陈。伏望 邸下。将臣此书。仰禀 大朝。仍命礼官。博议大臣及知礼之士而后审处之。俾礼典无失。人心无悔。千万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论 端懿嫔练事再书
伏以臣母老病沉笃之中。近又挟感添重。臣之受由救护。已过数日。而种种症情。有加无减。臣左右扶将。情理煎迫。决无离侧从宦之望。 书筵重任。不可一向虚带。玆不得不更伸疾痛之呼。仰干 仁孝之听。伏乞 邸下。特推终始之恩。亟赐镌递臣职名。使臣得以专意扶护。公私并幸。臣于向日。敢陈瞽说。妄论邸下不当为 端懿嫔行练一事。极知僭汰无所逃
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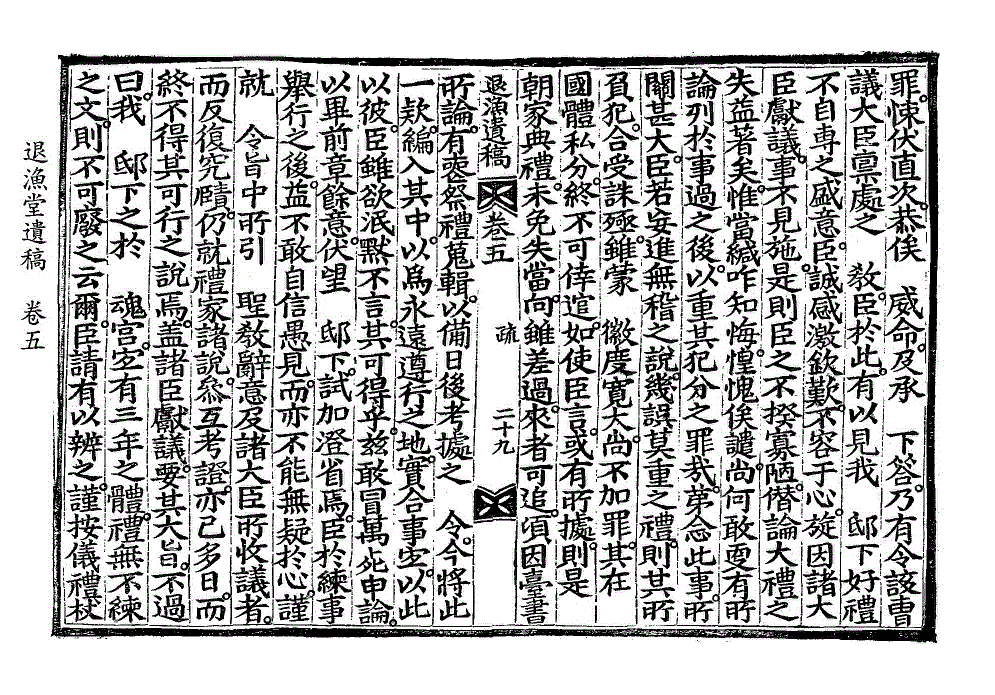 罪。悚伏直次。恭俟 威命。及承 下答。乃有令该曹议大臣禀处之 教。臣于此。有以见我 邸下好礼不自专之盛意。臣诚感激钦叹。不容于心。旋因诸大臣献议。事不见施。是则臣之不揆寡陋。僭论大礼之失益著矣。惟当缄咋知悔。惶愧俟谴。尚何敢更有所论列于事过之后。以重其犯分之罪哉。第念此事。所关甚大。臣若妄进无稽之说。几误莫重之礼。则其所负犯。合受诛殛。虽蒙 徽度宽大。尚不加罪。其在 国体私分。终不可倖逭。如使臣言。或有所据。则是 朝家典礼。未免失当。向虽差过。来者可追。顷因台书所论。有丧祭礼蒐辑。以备日后考据之 令。今将此一款。编入其中。以为永远遵行之地。实合事宜。以此以彼。臣虽欲泯默不言。其可得乎。玆敢冒万死申论。以毕前章馀意。伏望 邸下。试加澄省焉。臣于练事举行之后。益不敢自信愚见。而亦不能无疑于心。谨就 令旨中所引 圣教辞意及诸大臣所收议者。而反复究赜。仍就礼家诸说。参互考證。亦已多日。而终不得其可行之说焉。盖诸臣献议。要其大旨。不过曰。我 邸下之于 魂宫。宜有三年之体。礼无不练之文。则不可废之云尔。臣请有以辨之。谨按仪礼杖
罪。悚伏直次。恭俟 威命。及承 下答。乃有令该曹议大臣禀处之 教。臣于此。有以见我 邸下好礼不自专之盛意。臣诚感激钦叹。不容于心。旋因诸大臣献议。事不见施。是则臣之不揆寡陋。僭论大礼之失益著矣。惟当缄咋知悔。惶愧俟谴。尚何敢更有所论列于事过之后。以重其犯分之罪哉。第念此事。所关甚大。臣若妄进无稽之说。几误莫重之礼。则其所负犯。合受诛殛。虽蒙 徽度宽大。尚不加罪。其在 国体私分。终不可倖逭。如使臣言。或有所据。则是 朝家典礼。未免失当。向虽差过。来者可追。顷因台书所论。有丧祭礼蒐辑。以备日后考据之 令。今将此一款。编入其中。以为永远遵行之地。实合事宜。以此以彼。臣虽欲泯默不言。其可得乎。玆敢冒万死申论。以毕前章馀意。伏望 邸下。试加澄省焉。臣于练事举行之后。益不敢自信愚见。而亦不能无疑于心。谨就 令旨中所引 圣教辞意及诸大臣所收议者。而反复究赜。仍就礼家诸说。参互考證。亦已多日。而终不得其可行之说焉。盖诸臣献议。要其大旨。不过曰。我 邸下之于 魂宫。宜有三年之体。礼无不练之文。则不可废之云尔。臣请有以辨之。谨按仪礼杖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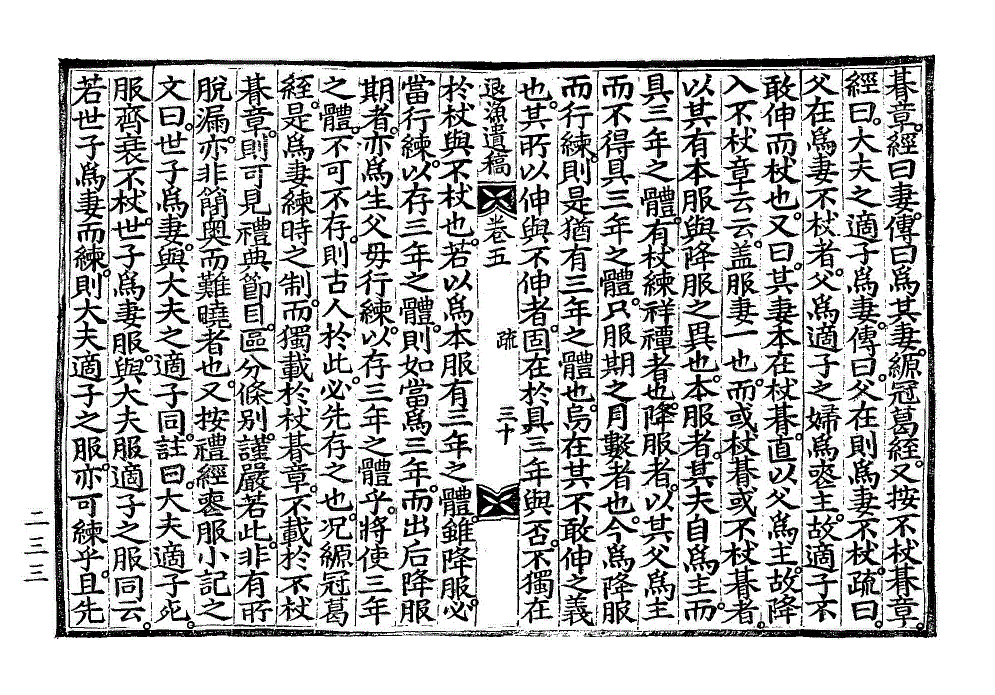 期章。经曰妻。传曰为其妻。縓冠葛绖。又按不杖期章。经曰。大夫之适子为妻。传曰。父在则为妻不杖。疏曰。父在为妻不杖者。父为适子之妇为丧主。故适子不敢伸而杖也。又曰。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为主。故降入不杖章云云。盖服妻一也。而或杖期或不杖期者。以其有本服与降服之异也。本服者。其夫自为主。而具三年之体。有杖练祥禫者也。降服者。以其父为主而不得具三年之体。只服期之月数者也。今为降服而行练。则是犹有三年之体也。乌在其不敢伸之义也。其所以伸与不伸者。固在于具三年与否。不独在于杖与不杖也。若以为本服有三年之体。虽降服。必当行练。以存三年之体。则如当为三年。而出后降服期者。亦为生父母行练。以存三年之体乎。将使三年之体。不可不存。则古人于此。必先存之也。况縓冠葛绖。是为妻练时之制。而独载于杖期章。不载于不杖期章。则可见礼典节目。区分条别。谨严若此。非有所脱漏。亦非简奥而难晓者也。又按礼经丧服小记之文曰。世子为妻。与大夫之适子同。注曰。大夫适子死。服齐衰不杖。世子为妻服。与大夫服适子之服同云。若世子为妻而练。则大夫适子之服。亦可练乎。且先
期章。经曰妻。传曰为其妻。縓冠葛绖。又按不杖期章。经曰。大夫之适子为妻。传曰。父在则为妻不杖。疏曰。父在为妻不杖者。父为适子之妇为丧主。故适子不敢伸而杖也。又曰。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为主。故降入不杖章云云。盖服妻一也。而或杖期或不杖期者。以其有本服与降服之异也。本服者。其夫自为主。而具三年之体。有杖练祥禫者也。降服者。以其父为主而不得具三年之体。只服期之月数者也。今为降服而行练。则是犹有三年之体也。乌在其不敢伸之义也。其所以伸与不伸者。固在于具三年与否。不独在于杖与不杖也。若以为本服有三年之体。虽降服。必当行练。以存三年之体。则如当为三年。而出后降服期者。亦为生父母行练。以存三年之体乎。将使三年之体。不可不存。则古人于此。必先存之也。况縓冠葛绖。是为妻练时之制。而独载于杖期章。不载于不杖期章。则可见礼典节目。区分条别。谨严若此。非有所脱漏。亦非简奥而难晓者也。又按礼经丧服小记之文曰。世子为妻。与大夫之适子同。注曰。大夫适子死。服齐衰不杖。世子为妻服。与大夫服适子之服同云。若世子为妻而练。则大夫适子之服。亦可练乎。且先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4H 页
 正臣宋浚吉之答故相臣李厚源书。有曰。大夫之长子。父在似不得为妻杖。不杖则恐无练禫节次云。此可谓深得礼意。而亦可为不练之證矣。夫先正道学礼识。非今之廷臣所敢望焉。则未知 朝家之所当取信者。在先正乎。在廷臣乎。以此等礼说之明的者观之。 邸下之于 魂宫。其可具三年之体乎否乎。其当为练乎否乎。事理晓然。不难知矣。凡丧。主其丧者主其祭。今 端懿嫔丧祭。我 殿下实主之。而遂行练祭。则是为 殿下练乎。 邸下练乎。 殿下无练而 邸下有练祭。则 殿下主之。而练则 邸下为之。是果合于礼乎。其名实不称。节目径庭。岂不为未安之甚者乎。收议中所引丧礼备要小祥条。父在为母与为妻云者。与本文旨意。迥然不同。盖父在二字。只属乎为母字。而不属乎为妻字。仪礼杖期条。经曰。父在为母。又曰。妻。此谓母服之三年。以父在而降为杖期。妻之服本杖期。故同载于杖期之中也。今以为妻二字。蒙上父在而观之。则是妻之服。亦若以父在故为杖期者然。此岂理也哉。噫。先王制礼。隆杀厚薄。截有等级。隆处不可杀。杀处不可隆。宜隆而杀。宜杀而隆。其失等耳。近来邦礼。率以隆厚为主。隆厚而
正臣宋浚吉之答故相臣李厚源书。有曰。大夫之长子。父在似不得为妻杖。不杖则恐无练禫节次云。此可谓深得礼意。而亦可为不练之證矣。夫先正道学礼识。非今之廷臣所敢望焉。则未知 朝家之所当取信者。在先正乎。在廷臣乎。以此等礼说之明的者观之。 邸下之于 魂宫。其可具三年之体乎否乎。其当为练乎否乎。事理晓然。不难知矣。凡丧。主其丧者主其祭。今 端懿嫔丧祭。我 殿下实主之。而遂行练祭。则是为 殿下练乎。 邸下练乎。 殿下无练而 邸下有练祭。则 殿下主之。而练则 邸下为之。是果合于礼乎。其名实不称。节目径庭。岂不为未安之甚者乎。收议中所引丧礼备要小祥条。父在为母与为妻云者。与本文旨意。迥然不同。盖父在二字。只属乎为母字。而不属乎为妻字。仪礼杖期条。经曰。父在为母。又曰。妻。此谓母服之三年。以父在而降为杖期。妻之服本杖期。故同载于杖期之中也。今以为妻二字。蒙上父在而观之。则是妻之服。亦若以父在故为杖期者然。此岂理也哉。噫。先王制礼。隆杀厚薄。截有等级。隆处不可杀。杀处不可隆。宜隆而杀。宜杀而隆。其失等耳。近来邦礼。率以隆厚为主。隆厚而退渔堂遗稿卷之五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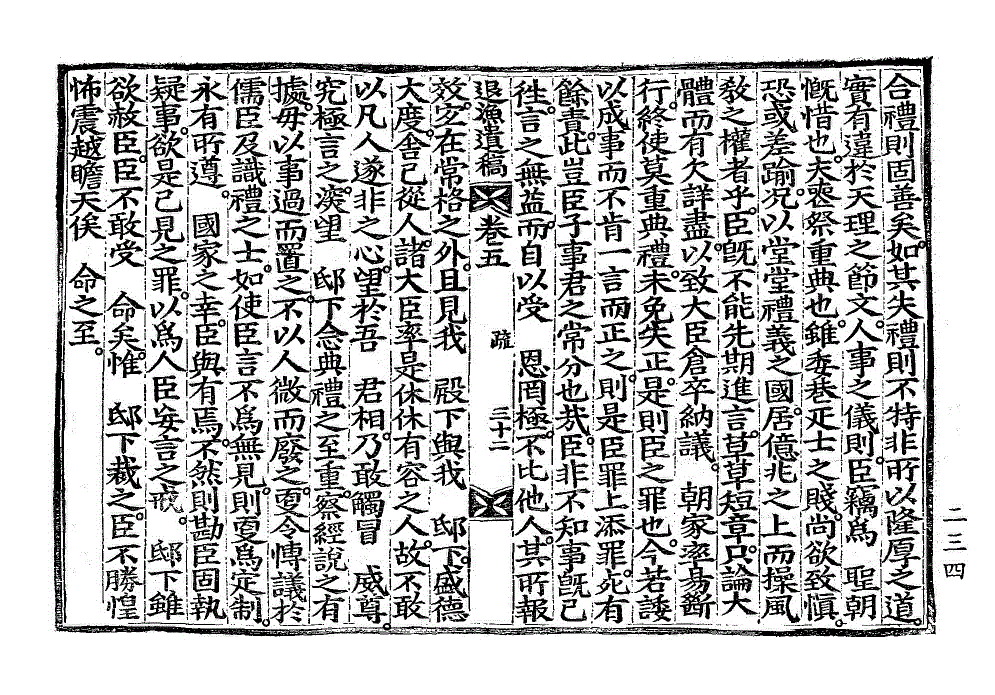 合礼则固善矣。如其失礼则不特非所以隆厚之道。实有违于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臣窃为 圣朝慨惜也。夫丧祭重典也。虽委巷疋士之贱。尚欲致慎。恐或差踰。况以堂堂礼义之国。居亿兆之上而操风教之权者乎。臣既不能先期进言。草草短章。只论大体而有欠详尽。以致大臣仓卒纳议。 朝家率易断行。终使莫重典礼。未免失正。是则臣之罪也。今若诿以成事而不肯一言而正之。则是臣罪上添罪。死有馀责。此岂臣子事君之常分也哉。臣非不知事既已往。言之无益。而自以受 恩罔极。不比他人。其所报效。宜在常格之外。且见我 殿下与我 邸下。盛德大度。舍己从人。诸大臣率是休休有容之人。故不敢以凡人遂非之心。望于吾 君相。乃敢触冒 威尊。究极言之。深望 邸下念典礼之至重。察经说之有据。毋以事过而置之。不以人微而废之。更令博议于儒臣及识礼之士。如使臣言不为无见。则更为定制。永有所遵。 国家之幸。臣与有焉。不然则勘臣固执疑事。欲是己见之罪。以为人臣妄言之戒。 邸下虽欲赦臣。臣不敢受 命矣。惟 邸下裁之。臣不胜惶怖震越瞻天俟 命之至。
合礼则固善矣。如其失礼则不特非所以隆厚之道。实有违于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臣窃为 圣朝慨惜也。夫丧祭重典也。虽委巷疋士之贱。尚欲致慎。恐或差踰。况以堂堂礼义之国。居亿兆之上而操风教之权者乎。臣既不能先期进言。草草短章。只论大体而有欠详尽。以致大臣仓卒纳议。 朝家率易断行。终使莫重典礼。未免失正。是则臣之罪也。今若诿以成事而不肯一言而正之。则是臣罪上添罪。死有馀责。此岂臣子事君之常分也哉。臣非不知事既已往。言之无益。而自以受 恩罔极。不比他人。其所报效。宜在常格之外。且见我 殿下与我 邸下。盛德大度。舍己从人。诸大臣率是休休有容之人。故不敢以凡人遂非之心。望于吾 君相。乃敢触冒 威尊。究极言之。深望 邸下念典礼之至重。察经说之有据。毋以事过而置之。不以人微而废之。更令博议于儒臣及识礼之士。如使臣言不为无见。则更为定制。永有所遵。 国家之幸。臣与有焉。不然则勘臣固执疑事。欲是己见之罪。以为人臣妄言之戒。 邸下虽欲赦臣。臣不敢受 命矣。惟 邸下裁之。臣不胜惶怖震越瞻天俟 命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