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疏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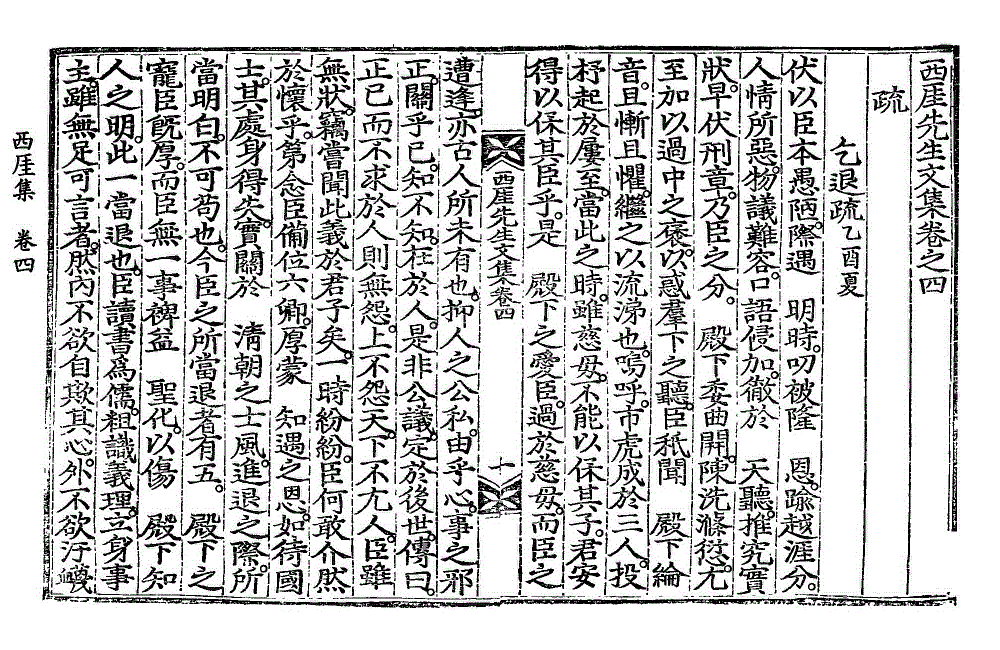 乞退疏(乙酉夏)
乞退疏(乙酉夏)伏以臣本愚陋。际遇 明时。叨被隆 恩。踰越涯分。人情所恶。物议难容。口语侵加。彻于 天听。推究实状。早伏刑草。乃臣之分。 殿下委曲开陈。洗涤愆尤。至加以过中之褒。以惑群下之听。臣秖闻 殿下纶音。且惭且惧。继之以流涕也。呜呼。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当此之时。虽慈母。不能以保其子。君安得以保其臣乎。是 殿下之爱臣。过于慈母。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也。抑人之公私。由乎心。事之邪正。关乎己。知不知。在于人。是非公议。定于后世。传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臣虽无状。窃尝闻此义于君子矣。一时纷纷。臣何敢介然于怀乎。第念臣备位六卿。厚蒙 知遇之恩。如待国士。其处身得失。实关于 清朝之士风。进退之际。所当明白。不可苟也。今臣之所当退者有五。 殿下之宠臣既厚。而臣无一事裨益 圣化。以伤 殿下知人之明。此一当退也。臣读书为儒。粗识义理。立身事主。虽无足可言者。然内不欲自欺其心。外不欲污蔑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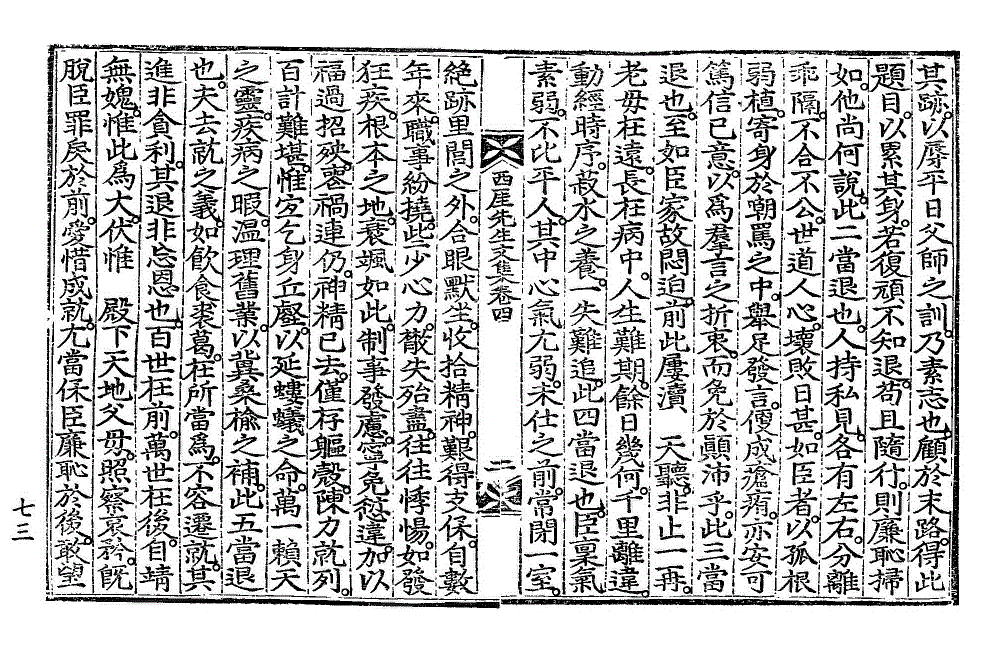 其迹。以辱平日父师之训。乃素志也。顾于末路。得此题目。以累其身。若复顽不知退。苟且随行。则廉耻扫如。他尚何说。此二当退也。人持私见。各有左右。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世道人心。坏败日甚。如臣者。以孤根弱植。寄身于嘲骂之中。举足发言。便成疮痏。亦安可笃信己意。以为群言之折衷。而免于颠沛乎。此三当退也。至如臣家故闷迫。前此屡渎 天听。非止一再。老母在远。长在病中。人生难期。馀日几何。千里离违。动经时序。菽水之养。一失难追。此四当退也。臣禀气素弱。不比平人。其中心气尤弱。未仕之前。常闭一室。绝迹里闾之外。合眼默坐。收拾精神。艰得支保。自数年来。职事纷挠。些少心力。散失殆尽。往往悸惕。如发狂疾。根本之地。衰飒如此。制事发虑。宁免愆违。加以福过招殃。丧祸连仍。神精已去。仅存躯壳。陈力就列。百计难堪。惟宜乞身兵壑。以延蝼蚁之命。万一赖天之灵。疾病之暇。温理旧业。以冀桑榆之补。此五当退也。夫去就之义。如饮食裘葛。在所当为。不容迁就。其进非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万世在后。自靖无愧。惟此为大。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照察哀矜。既脱臣罪戾于前。爱惜成就。尤当保臣廉耻于后。敢望
其迹。以辱平日父师之训。乃素志也。顾于末路。得此题目。以累其身。若复顽不知退。苟且随行。则廉耻扫如。他尚何说。此二当退也。人持私见。各有左右。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世道人心。坏败日甚。如臣者。以孤根弱植。寄身于嘲骂之中。举足发言。便成疮痏。亦安可笃信己意。以为群言之折衷。而免于颠沛乎。此三当退也。至如臣家故闷迫。前此屡渎 天听。非止一再。老母在远。长在病中。人生难期。馀日几何。千里离违。动经时序。菽水之养。一失难追。此四当退也。臣禀气素弱。不比平人。其中心气尤弱。未仕之前。常闭一室。绝迹里闾之外。合眼默坐。收拾精神。艰得支保。自数年来。职事纷挠。些少心力。散失殆尽。往往悸惕。如发狂疾。根本之地。衰飒如此。制事发虑。宁免愆违。加以福过招殃。丧祸连仍。神精已去。仅存躯壳。陈力就列。百计难堪。惟宜乞身兵壑。以延蝼蚁之命。万一赖天之灵。疾病之暇。温理旧业。以冀桑榆之补。此五当退也。夫去就之义。如饮食裘葛。在所当为。不容迁就。其进非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万世在后。自靖无愧。惟此为大。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照察哀矜。既脱臣罪戾于前。爱惜成就。尤当保臣廉耻于后。敢望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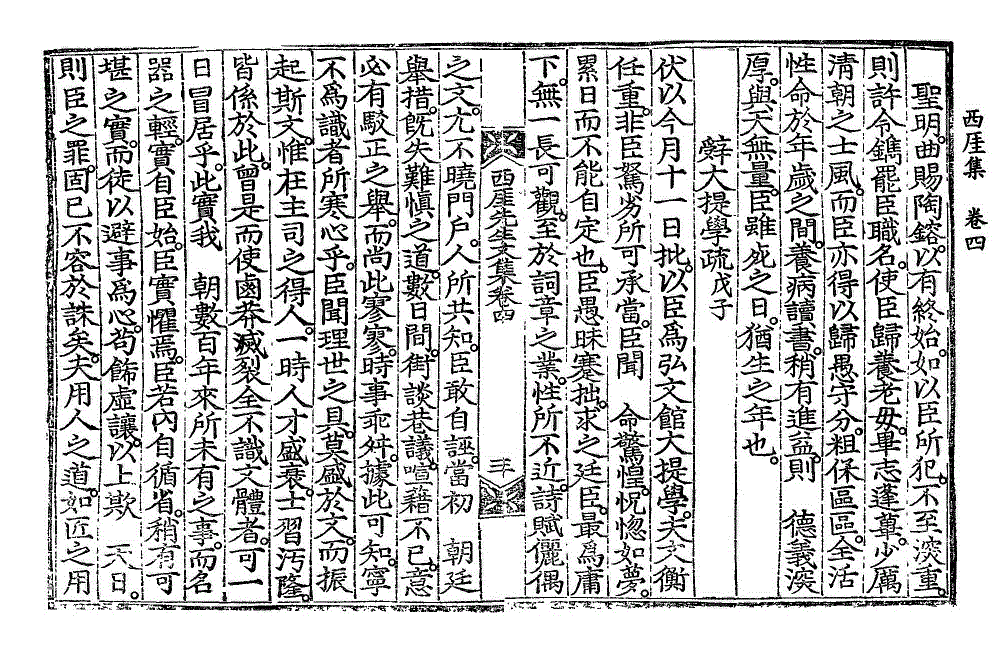 圣明。曲赐陶镕。以有终始。如以臣所犯。不至深重。则许令镌罢臣职名。使臣归养老母。毕志蓬荜。少厉清朝之士风。而臣亦得以归愚守分。粗保区区。全活性命于年岁之间。养病读书。稍有进益。则 德义深厚。与天无量。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圣明。曲赐陶镕。以有终始。如以臣所犯。不至深重。则许令镌罢臣职名。使臣归养老母。毕志蓬荜。少厉清朝之士风。而臣亦得以归愚守分。粗保区区。全活性命于年岁之间。养病读书。稍有进益。则 德义深厚。与天无量。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辞大提学疏(戊子)
伏以今月十一日批。以臣为弘文馆大提学。夫文衡任重。非臣驽劣所可承当。臣闻 命惊惶。恍惚如梦。累日而不能自定也。臣愚昧蹇拙。求之廷臣。最为庸下。无一长可观。至于词章之业。性所不近。诗赋俪偶之文。尤不晓门户。人所共知。臣敢自诬。当初 朝廷举措。既失难慎之道。数日间。街谈巷议。喧藉不已。意必有驳正之举。而尚此寥寥。时事乖舛。据此可知。宁不为识者所寒心乎。臣闻理世之具。莫盛于文。而振起斯文。惟在主司之得人。一时人才盛衰。士习污隆。皆系于此。曾是而使卤莽灭裂全不识文体者。可一日冒居乎。此实我 朝数百年来所未有之事。而名器之轻。实自臣始。臣实惧焉。臣若内自循省。稍有可堪之实。而徒以避事为心。苟饰虚让。以上欺 天日。则臣之罪。固已不容于诛矣。夫用人之道。如匠之用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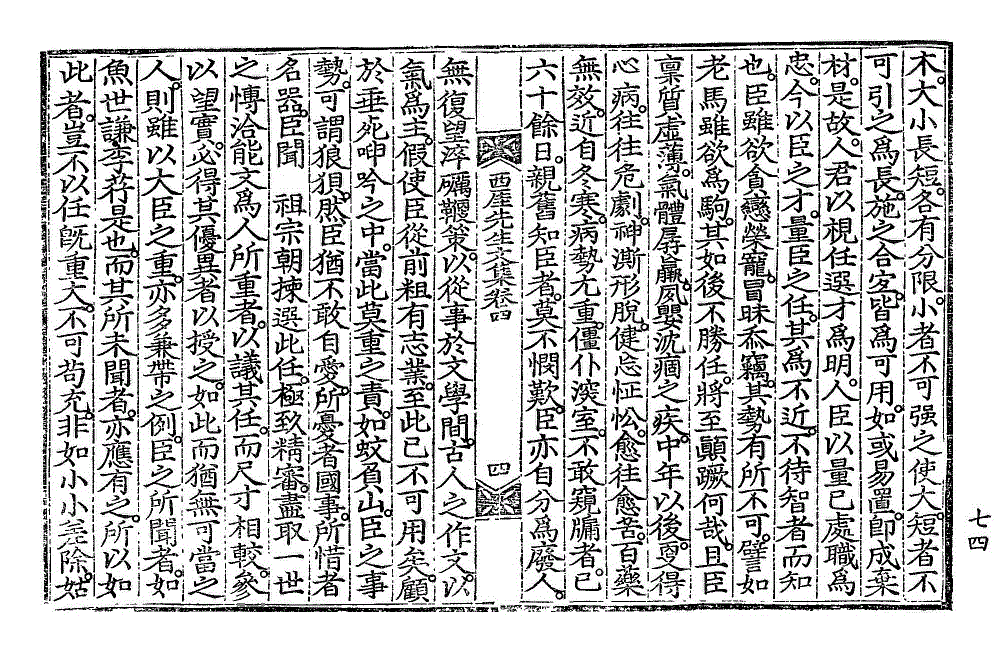 木。大小长短。各有分限。小者不可强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为长。施之合宜。皆为可用。如或易置。即成弃材。是故。人君以视任选才为明。人臣以量己处职为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为不近。不待智者而知也。臣虽欲贪恋荣宠。冒昧忝窃。其势有所不可。譬如老马虽欲为驹。其如后不胜任。将至颠蹶何哉。且臣禀质虚薄。气体孱羸。夙婴沈痼之疾。中年以后。更得心病。往往危剧。神澌形脱。健忘怔忪。愈往愈苦。百药无效。近自冬寒。病势尤重。僵仆深室。不敢窥牖者。已六十馀日。亲旧知臣者。莫不悯叹。臣亦自分为废人。无复望淬砺鞭策。以从事于文学间。古人之作文。以气为主。假使臣从前粗有志业。至此已不可用矣。顾于垂死呻吟之中。当此莫重之责。如蚊负山。臣之事势。可谓狼狈。然臣犹不敢自爱。所忧者国事。所惜者名器。臣闻 祖宗朝拣选此任。极致精审。尽取一世之博洽能文为人所重者。以议其任。而尺寸相较。参以望实。必得其优异者以授之。如此而犹无可当之人。则虽以大臣之重。亦多兼带之例。臣之所闻者。如鱼世谦,李荇是也。而其所未闻者。亦应有之。所以如此者。岂不以任既重大。不可苟充。非如小小差除。姑
木。大小长短。各有分限。小者不可强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为长。施之合宜。皆为可用。如或易置。即成弃材。是故。人君以视任选才为明。人臣以量己处职为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为不近。不待智者而知也。臣虽欲贪恋荣宠。冒昧忝窃。其势有所不可。譬如老马虽欲为驹。其如后不胜任。将至颠蹶何哉。且臣禀质虚薄。气体孱羸。夙婴沈痼之疾。中年以后。更得心病。往往危剧。神澌形脱。健忘怔忪。愈往愈苦。百药无效。近自冬寒。病势尤重。僵仆深室。不敢窥牖者。已六十馀日。亲旧知臣者。莫不悯叹。臣亦自分为废人。无复望淬砺鞭策。以从事于文学间。古人之作文。以气为主。假使臣从前粗有志业。至此已不可用矣。顾于垂死呻吟之中。当此莫重之责。如蚊负山。臣之事势。可谓狼狈。然臣犹不敢自爱。所忧者国事。所惜者名器。臣闻 祖宗朝拣选此任。极致精审。尽取一世之博洽能文为人所重者。以议其任。而尺寸相较。参以望实。必得其优异者以授之。如此而犹无可当之人。则虽以大臣之重。亦多兼带之例。臣之所闻者。如鱼世谦,李荇是也。而其所未闻者。亦应有之。所以如此者。岂不以任既重大。不可苟充。非如小小差除。姑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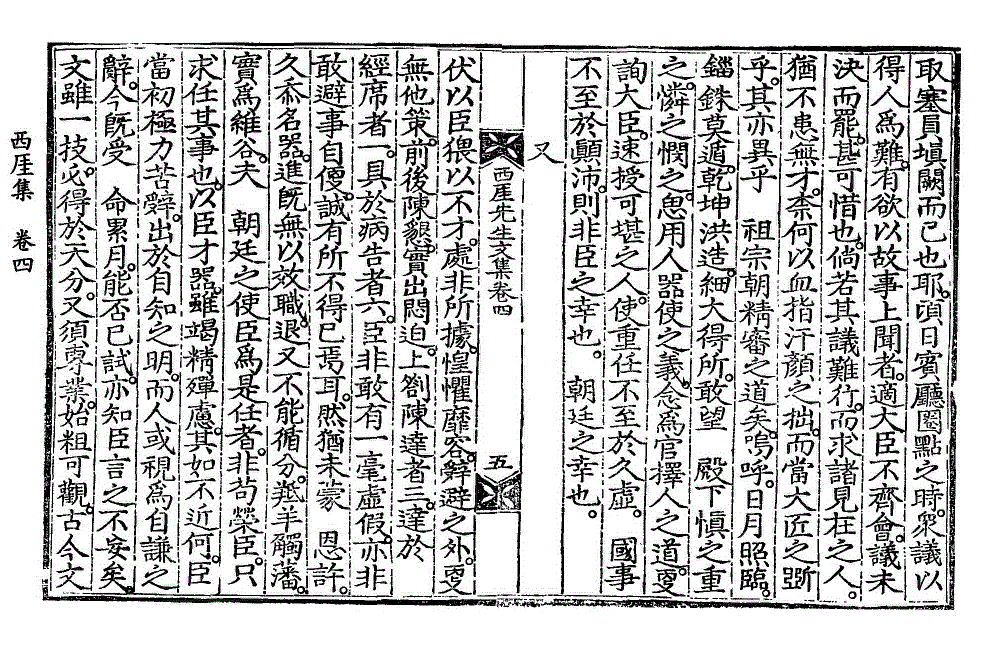 取塞员填阙而已也耶。顷日宾厅圈点之时。众议以得人为难。有欲以故事上闻者。适大臣不齐会。议未决而罢。甚可惜也。倘若其议难行。而求诸见在之人。犹不患无才。柰何以血指汗颜之拙。而当大匠之斲乎。其亦异乎 祖宗朝精审之道矣。呜呼。日月照临。锱铢莫遁。乾坤洪造。细大得所。敢望 殿下慎之重之。怜之悯之。思用人器使之义。念为官择人之道。更询大臣。速授可堪之人。使重任不至于久虚。 国事不至于颠沛。则非臣之幸也。 朝廷之幸也。
取塞员填阙而已也耶。顷日宾厅圈点之时。众议以得人为难。有欲以故事上闻者。适大臣不齐会。议未决而罢。甚可惜也。倘若其议难行。而求诸见在之人。犹不患无才。柰何以血指汗颜之拙。而当大匠之斲乎。其亦异乎 祖宗朝精审之道矣。呜呼。日月照临。锱铢莫遁。乾坤洪造。细大得所。敢望 殿下慎之重之。怜之悯之。思用人器使之义。念为官择人之道。更询大臣。速授可堪之人。使重任不至于久虚。 国事不至于颠沛。则非臣之幸也。 朝廷之幸也。辞大提学疏
伏以臣猥以不才。处非所据。惶惧靡容。辞避之外。更无他策。前后陈恳。实出闷迫。上劄陈达者三。达于 经席者一。具于病告者六。臣非敢有一毫虚假。亦非敢避事自便。诚有所不得已焉耳。然犹未蒙 恩许。久忝名器。进既无以效职。退又不能循分。羝羊触藩。实为维谷。夫 朝廷之使臣为是任者。非苟荣臣。只求任其事也。以臣才器。虽竭精殚虑。其如不近何。臣当初极力苦辞。出于自知之明。而人或视为自谦之辞。今既受 命累月。能否已试。亦知臣言之不妄矣。文虽一技。必得于天分。又须专业。始粗可观。古今文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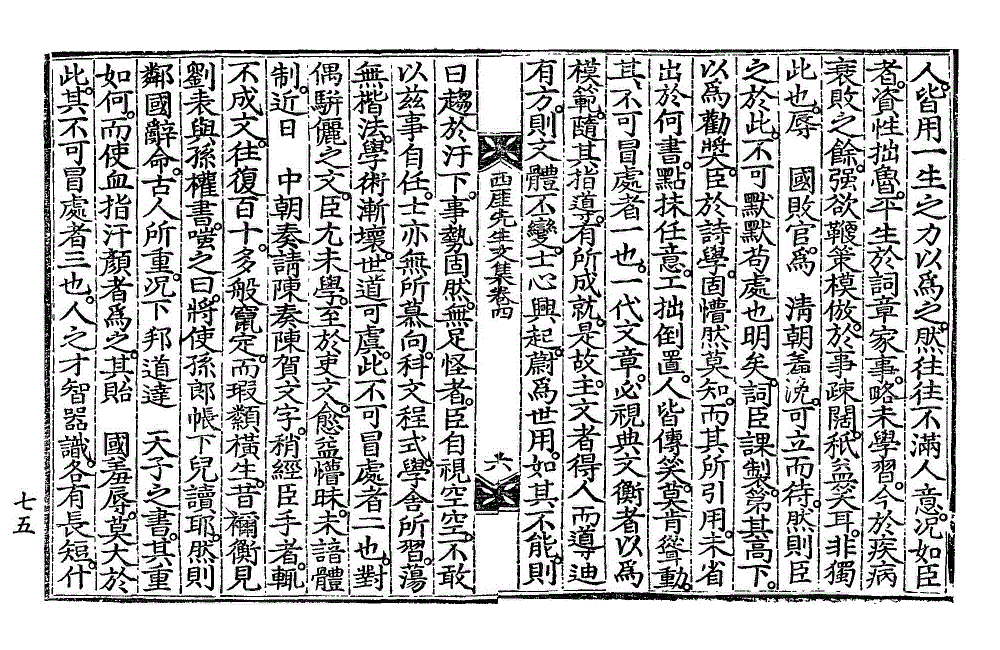 人。皆用一生之力以为之。然往往不满人意。况如臣者。资性拙鲁。平生于词章家事。略未学习。今于疾病衰败之馀。强欲鞭策模仿。于事疏阔。秖益笑耳。非独此也。辱 国败官。为 清朝羞浼。可立而待。然则臣之于此。不可默默苟处也明矣。词臣课制。第其高下。以为劝奖。臣于诗学。固懵然莫知。而其所引用。未省出于何书。点抹任意。工拙倒置。人皆传笑。莫肯耸动。其不可冒处者一也。一代文章。必视典文衡者以为模范。随其指导。有所成就。是故。主文者得人而导迪有方。则文体丕变。士心兴起。蔚为世用。如其不能。则日趋于污下。事势固然。无足怪者。臣自视空空。不敢以玆事自任。士亦无所慕向。科文程式。学舍所习。荡无楷法。学术渐坏。世道可虞。此不可冒处者二也。对偶骈俪之文。臣尤未学。至于吏文。愈益懵昧。未谙体制。近日 中朝奏请陈奏陈贺文字。稍经臣手者。辄不成文。往复百十。多般窜定。而瑕颣横生。昔祢衡见刘表与孙权书。嗤之曰。将使孙郎帐下儿读耶。然则邻国辞命。古人所重。况下邦道达 天子之书。其重如何。而使血指汗颜者为之。其贻 国羞辱。莫大于此。其不司冒处者三也。人之才智器识。各有长短。什
人。皆用一生之力以为之。然往往不满人意。况如臣者。资性拙鲁。平生于词章家事。略未学习。今于疾病衰败之馀。强欲鞭策模仿。于事疏阔。秖益笑耳。非独此也。辱 国败官。为 清朝羞浼。可立而待。然则臣之于此。不可默默苟处也明矣。词臣课制。第其高下。以为劝奖。臣于诗学。固懵然莫知。而其所引用。未省出于何书。点抹任意。工拙倒置。人皆传笑。莫肯耸动。其不可冒处者一也。一代文章。必视典文衡者以为模范。随其指导。有所成就。是故。主文者得人而导迪有方。则文体丕变。士心兴起。蔚为世用。如其不能。则日趋于污下。事势固然。无足怪者。臣自视空空。不敢以玆事自任。士亦无所慕向。科文程式。学舍所习。荡无楷法。学术渐坏。世道可虞。此不可冒处者二也。对偶骈俪之文。臣尤未学。至于吏文。愈益懵昧。未谙体制。近日 中朝奏请陈奏陈贺文字。稍经臣手者。辄不成文。往复百十。多般窜定。而瑕颣横生。昔祢衡见刘表与孙权书。嗤之曰。将使孙郎帐下儿读耶。然则邻国辞命。古人所重。况下邦道达 天子之书。其重如何。而使血指汗颜者为之。其贻 国羞辱。莫大于此。其不司冒处者三也。人之才智器识。各有长短。什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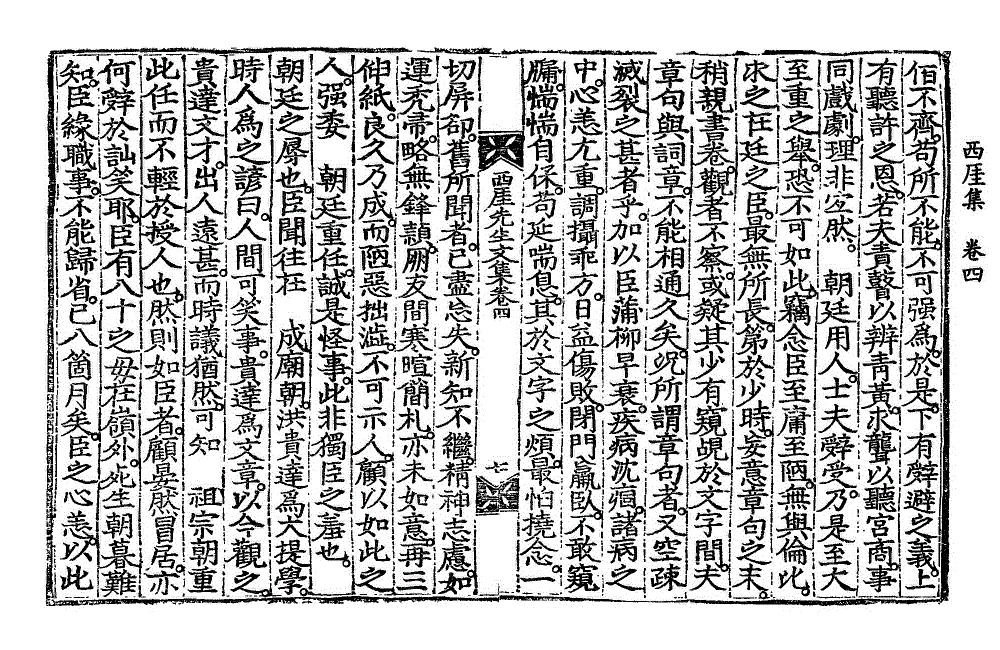 佰不齐。苟所不能。不可强为。于是。下有辞避之义。上有听许之恩。若夫责瞽以辨青黄。求聋以听宫商。事同戏剧。理非宜然。 朝廷用人。士夫辞受。乃是至大至重之举。恐不可如此。窃念臣至庸至陋。无与伦比。求之在廷之臣。最无所长。第于少时。妄意章句之末。稍亲书卷。观者不察。或疑其少有窥觇于文字间。夫章句与词章。不能相通久矣。况所谓章句者。又空疏灭裂之甚者乎。加以臣蒲柳早衰。疾病沈痼。诸病之中。心恙尤重。调摄乖方。日益伤败。闭门羸卧。不敢窥牖。惴惴自保。苟延喘息。其于文字之烦。最怕挠念。一切屏却。旧所闻者。已尽忘失。新知不继。精神志虑。如运秃帚。略无锋颖。朋友间寒暄简札。亦未如意。再三伸纸。良久乃成。而陋恶拙涩。不可示人。顾以如此之人。强委 朝廷重任。诚是怪事。此非独臣之羞也。 朝廷之辱也。臣闻往在 成庙朝。洪贵达为大提学。时人为之谚曰。人间可笑事。贵达为文章。以今观之。贵达文才。出人远甚。而时议犹然。可知 祖宗朝重此任而不轻于授人也。然则如臣者。顾晏然冒居。亦何辞于讪笑耶。臣有八十之母在岭外。死生朝暮难知。臣缘职事。不能归省。已八个月矣。臣之心恙。以此
佰不齐。苟所不能。不可强为。于是。下有辞避之义。上有听许之恩。若夫责瞽以辨青黄。求聋以听宫商。事同戏剧。理非宜然。 朝廷用人。士夫辞受。乃是至大至重之举。恐不可如此。窃念臣至庸至陋。无与伦比。求之在廷之臣。最无所长。第于少时。妄意章句之末。稍亲书卷。观者不察。或疑其少有窥觇于文字间。夫章句与词章。不能相通久矣。况所谓章句者。又空疏灭裂之甚者乎。加以臣蒲柳早衰。疾病沈痼。诸病之中。心恙尤重。调摄乖方。日益伤败。闭门羸卧。不敢窥牖。惴惴自保。苟延喘息。其于文字之烦。最怕挠念。一切屏却。旧所闻者。已尽忘失。新知不继。精神志虑。如运秃帚。略无锋颖。朋友间寒暄简札。亦未如意。再三伸纸。良久乃成。而陋恶拙涩。不可示人。顾以如此之人。强委 朝廷重任。诚是怪事。此非独臣之羞也。 朝廷之辱也。臣闻往在 成庙朝。洪贵达为大提学。时人为之谚曰。人间可笑事。贵达为文章。以今观之。贵达文才。出人远甚。而时议犹然。可知 祖宗朝重此任而不轻于授人也。然则如臣者。顾晏然冒居。亦何辞于讪笑耶。臣有八十之母在岭外。死生朝暮难知。臣缘职事。不能归省。已八个月矣。臣之心恙。以此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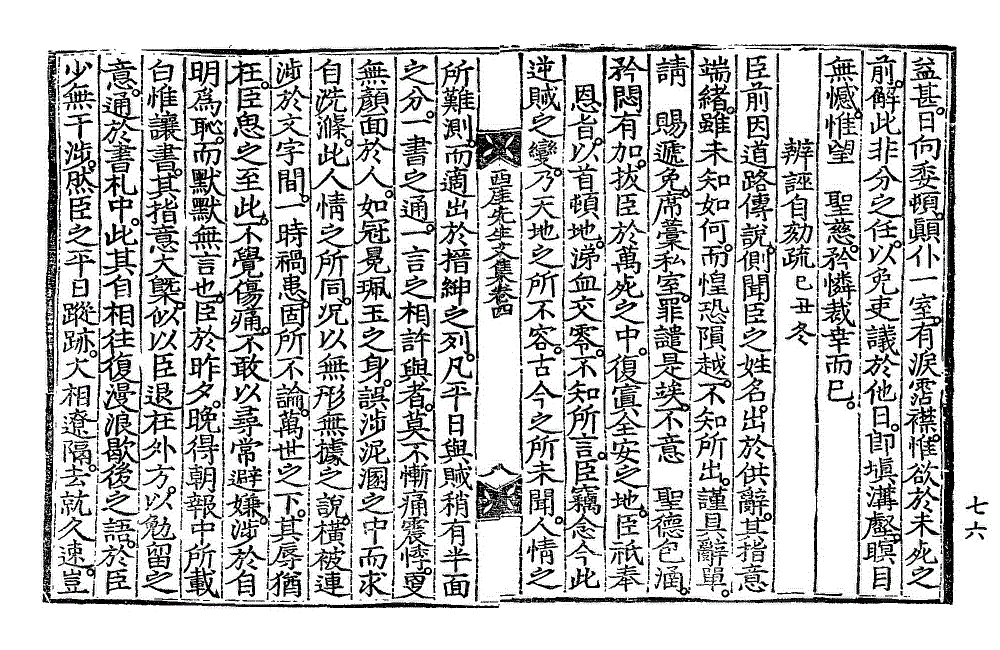 益甚。日向委顿。颠仆一室。有泪沾襟。惟欲于未死之前。解此非分之任。以免吏议于他日。即填沟壑。瞑目无憾。惟望 圣慈。矜怜裁幸而已。
益甚。日向委顿。颠仆一室。有泪沾襟。惟欲于未死之前。解此非分之任。以免吏议于他日。即填沟壑。瞑目无憾。惟望 圣慈。矜怜裁幸而已。辨诬自劾疏(己丑冬)
臣前因道路传说。侧闻臣之姓名。出于供辞。其指意端绪。虽未知如何。而惶恐陨越。不知所出。谨具辞单。请 赐递免。席藁私室。罪谴是俟。不意 圣德包涵。矜闷有加。拔臣于万死之中。复寘全安之地。臣祇奉 恩旨。以首顿地。涕血交零。不知所言。臣窃念今此逆贼之变。乃天地之所不容。古今之所未闻。人情之所难测。而适出于搢绅之列。凡平日与贼稍有半面之分。一书之通。一言之相许与者。莫不惭痛震悸。更无颜面于人。如冠冕佩玉之身。误涉泥溷之中而求自洗涤。此人情之所同。况以无形无据之说。横被连涉于文字间。一时祸患。固所不论。万世之下。其辱犹在。臣思之至此。不觉伤痛。不敢以寻常避嫌。涉于自明为耻。而默默无言也。臣于昨夕。晚得朝报中所载白惟让书。其指意大槩。似以臣退在外方。以勉留之意。通于书札中。此其自相往复漫浪歇后之语。于臣少无干涉。然臣之平日踪迹。大相辽隔。去就久速。岂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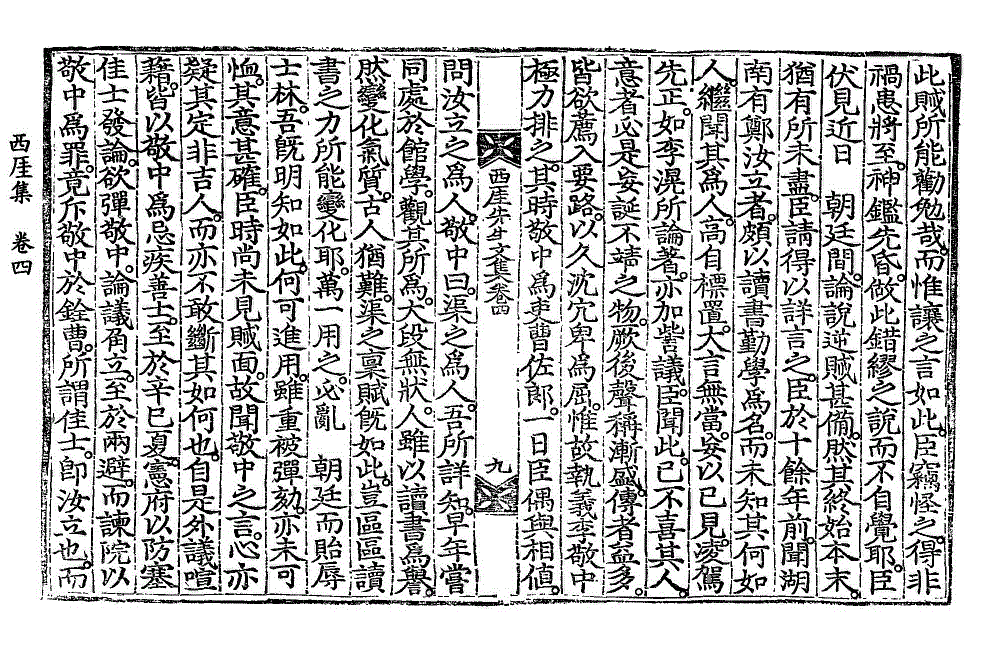 此贼所能劝勉哉。而惟让之言如此。臣窃怪之。得非祸患将至。神鉴先昏。做此错缪之说而不自觉耶。臣伏见近日 朝廷间。论说逆贼甚备。然其终始本末。犹有所未尽。臣请得以详言之。臣于十馀年前。闻湖南有郑汝立者。颇以读书勤学为名。而未知其何如人。继闻其为人。高自标置。大言无当。妄以己见。凌驾先正。如李滉所论著。亦加訾议。臣闻此。已不喜其人。意者必是妄诞不靖之物。厥后声称渐盛。传者益多。皆欲荐入要路。以久沈冗卑为屈。惟故执义李敬中极力排之。其时敬中为吏曹佐郎。一日臣偶与相值。问汝立之为人。敬中曰。渠之为人。吾所详知。早年尝同处于馆学。观其所为。大段无状。人虽以读书为誉。然变化气质。古人犹难。渠之禀赋既如此。岂区区读书之力所能变化耶。万一用之。必乱 朝廷而贻辱士林。吾既明知如此。何可进用。虽重被弹劾。亦未可恤。其意甚确。臣时尚未见贼面。故闻敬中之言。心亦疑其定非吉人。而亦不敢断其如何也。自是外议喧藉。皆以敬中为忌疾善士。至于辛巳夏。宪府以防塞佳士发论。欲弹敬中。论议角立。至于两避。而谏院以敬中为罪。竟斥敬中于铨曹。所谓佳士。即汝立也。而
此贼所能劝勉哉。而惟让之言如此。臣窃怪之。得非祸患将至。神鉴先昏。做此错缪之说而不自觉耶。臣伏见近日 朝廷间。论说逆贼甚备。然其终始本末。犹有所未尽。臣请得以详言之。臣于十馀年前。闻湖南有郑汝立者。颇以读书勤学为名。而未知其何如人。继闻其为人。高自标置。大言无当。妄以己见。凌驾先正。如李滉所论著。亦加訾议。臣闻此。已不喜其人。意者必是妄诞不靖之物。厥后声称渐盛。传者益多。皆欲荐入要路。以久沈冗卑为屈。惟故执义李敬中极力排之。其时敬中为吏曹佐郎。一日臣偶与相值。问汝立之为人。敬中曰。渠之为人。吾所详知。早年尝同处于馆学。观其所为。大段无状。人虽以读书为誉。然变化气质。古人犹难。渠之禀赋既如此。岂区区读书之力所能变化耶。万一用之。必乱 朝廷而贻辱士林。吾既明知如此。何可进用。虽重被弹劾。亦未可恤。其意甚确。臣时尚未见贼面。故闻敬中之言。心亦疑其定非吉人。而亦不敢断其如何也。自是外议喧藉。皆以敬中为忌疾善士。至于辛巳夏。宪府以防塞佳士发论。欲弹敬中。论议角立。至于两避。而谏院以敬中为罪。竟斥敬中于铨曹。所谓佳士。即汝立也。而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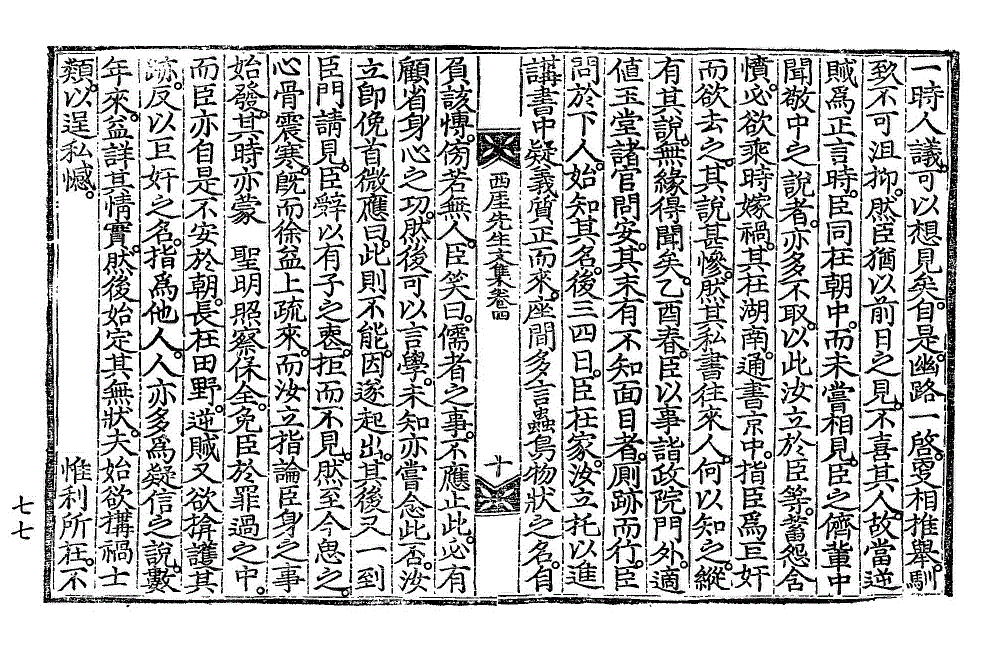 一时人议。可以想见矣。自是。幽路一启。更相推举。驯致不可沮抑。然臣犹以前日之见。不喜其人。故当逆贼为正言时。臣同在朝中。而未尝相见。臣之侪辈中闻敬中之说者。亦多不取。以此汝立于臣等。蓄怨含愤。必欲乘时嫁祸。其在湖南。通书京中。指臣为巨奸而欲去之。其说甚惨。然其私书往来人。何以知之。纵有其说。无缘得闻矣。乙酉春。臣以事诣政院门外。适值玉堂诸官问安。其末有不知面目者。厕迹而行。臣问于下人。始知其名。后三四日。臣在家。汝立托以进讲书中疑义质正而来。座间多言虫鸟物状之名。自负该博。傍若无人。臣笑曰。儒者之事。不应止此。必有顾省身心之功。然后可以言学。未知亦尝念此否。汝立即俛首微应曰。此则不能。因遂起出。其后又一到臣门请见。臣辞以有子之丧。拒而不见。然至今思之。心骨震寒。既而徐益上疏来。而汝立指论臣身之事始发。其时亦蒙 圣明照察保全。免臣于罪过之中。而臣亦自是不安于朝。长在田野。逆贼又欲掩护其迹。反以巨奸之名。指为他人。人亦多为疑信之说。数年来。益详其情实。然后始定其无状。夫始欲搆祸士类。以逞私憾。▣▣▣▣▣▣▣▣▣▣惟利所在。不
一时人议。可以想见矣。自是。幽路一启。更相推举。驯致不可沮抑。然臣犹以前日之见。不喜其人。故当逆贼为正言时。臣同在朝中。而未尝相见。臣之侪辈中闻敬中之说者。亦多不取。以此汝立于臣等。蓄怨含愤。必欲乘时嫁祸。其在湖南。通书京中。指臣为巨奸而欲去之。其说甚惨。然其私书往来人。何以知之。纵有其说。无缘得闻矣。乙酉春。臣以事诣政院门外。适值玉堂诸官问安。其末有不知面目者。厕迹而行。臣问于下人。始知其名。后三四日。臣在家。汝立托以进讲书中疑义质正而来。座间多言虫鸟物状之名。自负该博。傍若无人。臣笑曰。儒者之事。不应止此。必有顾省身心之功。然后可以言学。未知亦尝念此否。汝立即俛首微应曰。此则不能。因遂起出。其后又一到臣门请见。臣辞以有子之丧。拒而不见。然至今思之。心骨震寒。既而徐益上疏来。而汝立指论臣身之事始发。其时亦蒙 圣明照察保全。免臣于罪过之中。而臣亦自是不安于朝。长在田野。逆贼又欲掩护其迹。反以巨奸之名。指为他人。人亦多为疑信之说。数年来。益详其情实。然后始定其无状。夫始欲搆祸士类。以逞私憾。▣▣▣▣▣▣▣▣▣▣惟利所在。不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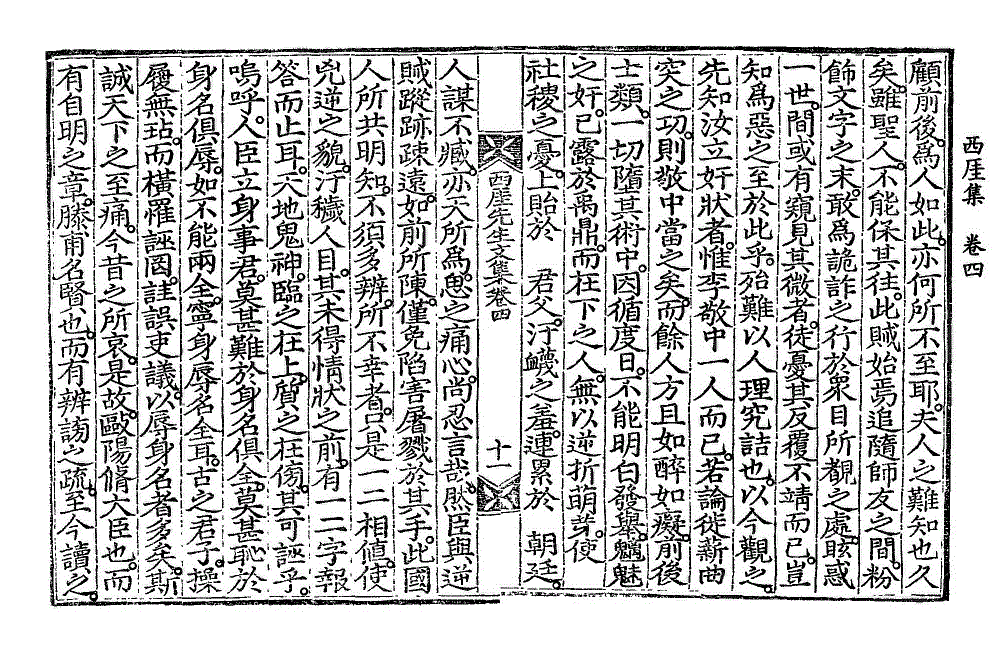 顾前后。为人如此。亦何所不至耶。夫人之难知也久矣。虽圣人。不能保其往。此贼始焉追随师友之间。粉饰文字之末。敢为诡诈之行于众目所睹之处。眩惑一世。间或有窥见其微者。徒忧其反覆不靖而已。岂知为恶之至于此乎。殆难以人理究诘也。以今观之。先知汝立奸状者。惟李敬中一人而已。若论徙薪曲突之功。则敬中当之矣。而馀人方且如醉如痴。前后士类。一切堕其术中。因循度日。不能明白发举。魑魅之奸。已露于禹鼎。而在下之人。无以逆折萌芽。使 社稷之忧。上贻于 君父。污蔑之羞。连累于 朝廷。人谋不臧。亦天所为。思之痛心。尚忍言哉。然臣与逆贼踪迹疏远。如前所陈。仅免陷害屠戮于其手。此国人所共明知。不须多辨。所不幸者。只是一二相值。使凶逆之貌。污秽人目。其未得情状之前。有一二字报答而止耳。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其可诬乎。呜呼。人臣立身事君。莫甚难于身名俱全。莫甚耻于身名俱辱。如不能两全。宁身辱名全耳。古之君子。操履无玷。而横罹诬罔。诖误吏议。以辱身名者多矣。斯诚天下之至痛。今昔之所哀。是故。驱阳修大臣也。而有自明之章。滕甫名贤也。而有辨谤之疏。至今读之。
顾前后。为人如此。亦何所不至耶。夫人之难知也久矣。虽圣人。不能保其往。此贼始焉追随师友之间。粉饰文字之末。敢为诡诈之行于众目所睹之处。眩惑一世。间或有窥见其微者。徒忧其反覆不靖而已。岂知为恶之至于此乎。殆难以人理究诘也。以今观之。先知汝立奸状者。惟李敬中一人而已。若论徙薪曲突之功。则敬中当之矣。而馀人方且如醉如痴。前后士类。一切堕其术中。因循度日。不能明白发举。魑魅之奸。已露于禹鼎。而在下之人。无以逆折萌芽。使 社稷之忧。上贻于 君父。污蔑之羞。连累于 朝廷。人谋不臧。亦天所为。思之痛心。尚忍言哉。然臣与逆贼踪迹疏远。如前所陈。仅免陷害屠戮于其手。此国人所共明知。不须多辨。所不幸者。只是一二相值。使凶逆之貌。污秽人目。其未得情状之前。有一二字报答而止耳。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其可诬乎。呜呼。人臣立身事君。莫甚难于身名俱全。莫甚耻于身名俱辱。如不能两全。宁身辱名全耳。古之君子。操履无玷。而横罹诬罔。诖误吏议。以辱身名者多矣。斯诚天下之至痛。今昔之所哀。是故。驱阳修大臣也。而有自明之章。滕甫名贤也。而有辨谤之疏。至今读之。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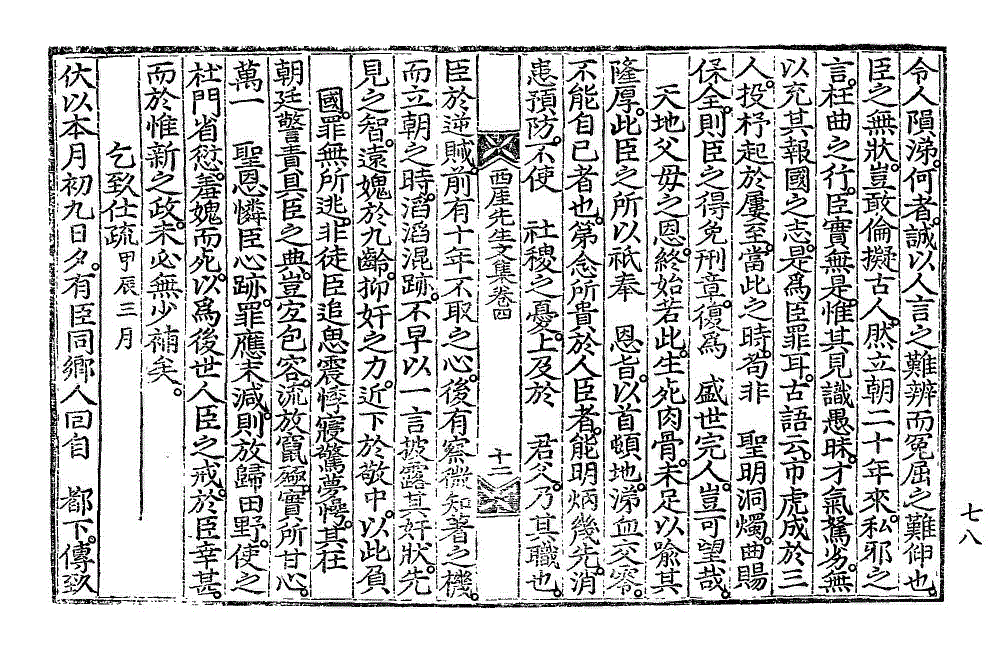 令人陨涕。何者。诚以人言之难辨而冤屈之难伸也。臣之无状。岂敢伦拟古人。然立朝二十年来。私邪之言。枉曲之行。臣实无是。惟其见识愚昩。才气驽劣。无以充其报国之志。是为臣罪耳。古语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当此之时。苟非 圣明洞烛。曲赐保全。则臣之得免刑章。复为 盛世完人。岂可望哉。 天地父母之恩。终始若此。生死肉骨。未足以喻其隆厚。此臣之所以祇奉 恩旨。以首顿地。涕血交零。不能自已者也。第念所贵于人臣者。能明炳几先。消患预防。不使 社稷之忧。上及于 君父。乃其职也。臣于逆贼。前有十年不取之心。后有察微知著之机。而立朝之时。滔滔混迹。不早以乛言披露其奸状。先见之智。远愧于九龄。抑奸之力。近下于敬中。以此负 国。罪无所逃。非徒臣追思震悸寝惊梦愕。其在 朝廷警责具臣之典。岂宜包容。流放窜殛。实所甘心。万一 圣恩怜臣心迹。罪应末减。则放归田野。使之杜门省愆。羞愧而死。以为后世人臣之戒。于臣幸甚。而于惟新之政。未必无少补矣。
令人陨涕。何者。诚以人言之难辨而冤屈之难伸也。臣之无状。岂敢伦拟古人。然立朝二十年来。私邪之言。枉曲之行。臣实无是。惟其见识愚昩。才气驽劣。无以充其报国之志。是为臣罪耳。古语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当此之时。苟非 圣明洞烛。曲赐保全。则臣之得免刑章。复为 盛世完人。岂可望哉。 天地父母之恩。终始若此。生死肉骨。未足以喻其隆厚。此臣之所以祇奉 恩旨。以首顿地。涕血交零。不能自已者也。第念所贵于人臣者。能明炳几先。消患预防。不使 社稷之忧。上及于 君父。乃其职也。臣于逆贼。前有十年不取之心。后有察微知著之机。而立朝之时。滔滔混迹。不早以乛言披露其奸状。先见之智。远愧于九龄。抑奸之力。近下于敬中。以此负 国。罪无所逃。非徒臣追思震悸寝惊梦愕。其在 朝廷警责具臣之典。岂宜包容。流放窜殛。实所甘心。万一 圣恩怜臣心迹。罪应末减。则放归田野。使之杜门省愆。羞愧而死。以为后世人臣之戒。于臣幸甚。而于惟新之政。未必无少补矣。乞致仕疏(甲辰三月)
伏以本月初九日夕。有臣同乡人回自 都下。传致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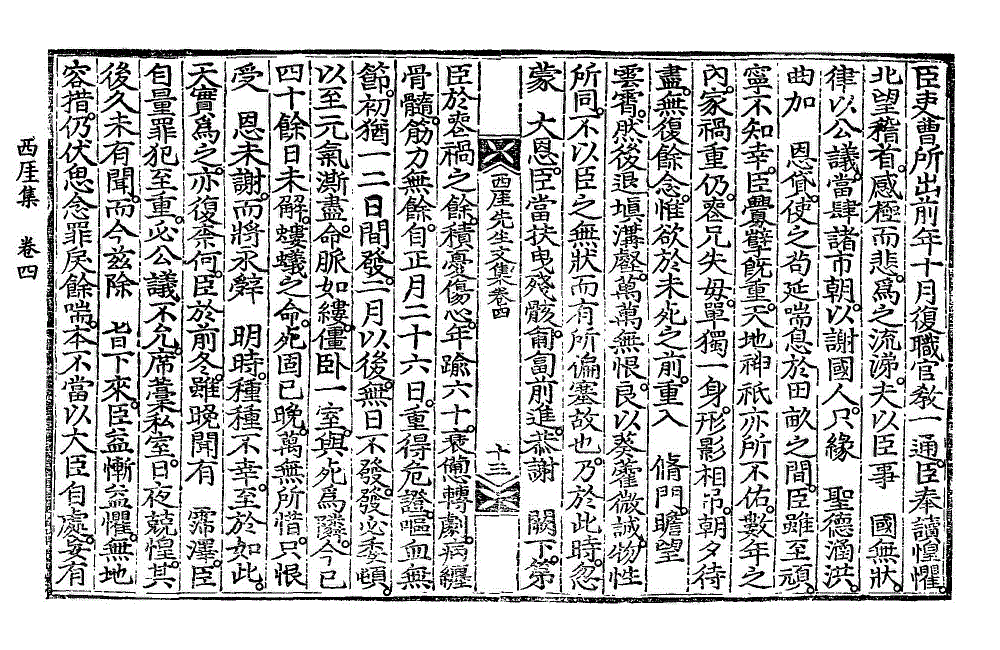 臣吏曹所出前年十月复职官教一通。臣奉读惶惧。北望稽首。感极而悲。为之流涕。夫以臣事 国无状。律以公议。当肆诸市朝。以谢国人。只缘 圣德涵洪。曲加 恩贷。使之苟延喘息于田亩之间。臣虽至顽。宁不知幸。臣衅孽既重。天地神祇亦所不佑。数年之内。家祸重仍。丧兄失母。单独一身。形影相吊。朝夕待尽。无复馀念。惟欲于未死之前。重入 修门。瞻望 云霄。然后退填沟壑。万万无恨。良以葵藿微诚。物性所同。不以臣之无状而有所偏塞故也。乃于此时。忽蒙 大恩。臣当扶曳残骸。匍匐前进。恭谢 阙下。第臣于丧祸之馀。积忧伤心。年踰六十。衰惫转剧。病缠骨髓。筋力无馀。自正月二十六日。重得危證。呕血无节。初犹一二日间发。二月以后。无日不发。发必委顿。以至元气澌尽。命脉如缕。僵卧一室。与死为邻。今已四十馀日未解。蝼蚁之命。死固已晚。万无所惜。只恨受 恩未谢。而将永辞 明时。种种不幸。至于如此。天实为之。亦复柰何。臣于前冬。虽晚闻有 霈泽。臣自量罪犯至重。必公议不允。席藁私室。日夜兢惶。其后久未有闻。而今玆除 旨下来。臣益惭益惧。无地容措。仍伏思念罪戾馀喘。本不当以大臣自处。妄有
臣吏曹所出前年十月复职官教一通。臣奉读惶惧。北望稽首。感极而悲。为之流涕。夫以臣事 国无状。律以公议。当肆诸市朝。以谢国人。只缘 圣德涵洪。曲加 恩贷。使之苟延喘息于田亩之间。臣虽至顽。宁不知幸。臣衅孽既重。天地神祇亦所不佑。数年之内。家祸重仍。丧兄失母。单独一身。形影相吊。朝夕待尽。无复馀念。惟欲于未死之前。重入 修门。瞻望 云霄。然后退填沟壑。万万无恨。良以葵藿微诚。物性所同。不以臣之无状而有所偏塞故也。乃于此时。忽蒙 大恩。臣当扶曳残骸。匍匐前进。恭谢 阙下。第臣于丧祸之馀。积忧伤心。年踰六十。衰惫转剧。病缠骨髓。筋力无馀。自正月二十六日。重得危證。呕血无节。初犹一二日间发。二月以后。无日不发。发必委顿。以至元气澌尽。命脉如缕。僵卧一室。与死为邻。今已四十馀日未解。蝼蚁之命。死固已晚。万无所惜。只恨受 恩未谢。而将永辞 明时。种种不幸。至于如此。天实为之。亦复柰何。臣于前冬。虽晚闻有 霈泽。臣自量罪犯至重。必公议不允。席藁私室。日夜兢惶。其后久未有闻。而今玆除 旨下来。臣益惭益惧。无地容措。仍伏思念罪戾馀喘。本不当以大臣自处。妄有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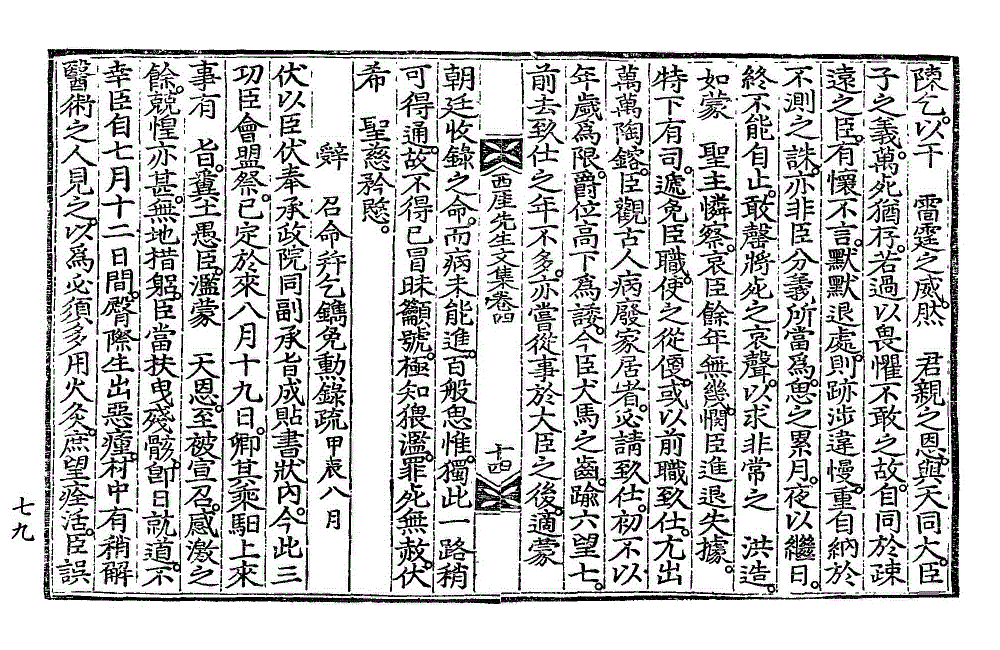 陈乞。以干 雷霆之威。然 君亲之恩。与天同大。臣子之义。万死犹存。若过以畏惧不敢之故。自同于疏远之臣。有怀不言。默默退处。则迹涉违慢。重自纳于不测之诛。亦非臣分义所当为。思之累月。夜以继日。终不能自止。敢罄将死之哀声。以求非常之 洪造。如蒙 圣主怜察。哀臣馀年无几。悯臣进退失据。 特下有司。递免臣职。使之从便。或以前职致仕。尤出万万陶镕。臣观古人病废家居者。必请致仕。初不以年岁为限。爵位高下为诿。今臣犬马之齿。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年不多。亦尝从事于大臣之后。适蒙 朝廷收录之命。而病未能进。百般思惟。独此一路稍可得通。故不得已冒昧吁号。极知猥滥。罪死无赦。伏希 圣慈矜悯。
陈乞。以干 雷霆之威。然 君亲之恩。与天同大。臣子之义。万死犹存。若过以畏惧不敢之故。自同于疏远之臣。有怀不言。默默退处。则迹涉违慢。重自纳于不测之诛。亦非臣分义所当为。思之累月。夜以继日。终不能自止。敢罄将死之哀声。以求非常之 洪造。如蒙 圣主怜察。哀臣馀年无几。悯臣进退失据。 特下有司。递免臣职。使之从便。或以前职致仕。尤出万万陶镕。臣观古人病废家居者。必请致仕。初不以年岁为限。爵位高下为诿。今臣犬马之齿。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年不多。亦尝从事于大臣之后。适蒙 朝廷收录之命。而病未能进。百般思惟。独此一路稍可得通。故不得已冒昧吁号。极知猥滥。罪死无赦。伏希 圣慈矜悯。辞 召命并乞镌免勋录疏(甲辰八月)
伏以臣伏奉承政院同副承旨成贴书状内。今此三功臣会盟祭。已定于来八月十九日。卿其乘驲上来事有 旨。粪土愚臣。滥蒙 天恩。至被宣召。感激之馀。兢惶亦甚。无地措躬。臣当扶曳残骸。即日就道。不幸臣自七月十二日间。臀际生出恶尰。村中有稍解医术之人见之。以为必须多用火灸。庶望痊活。臣误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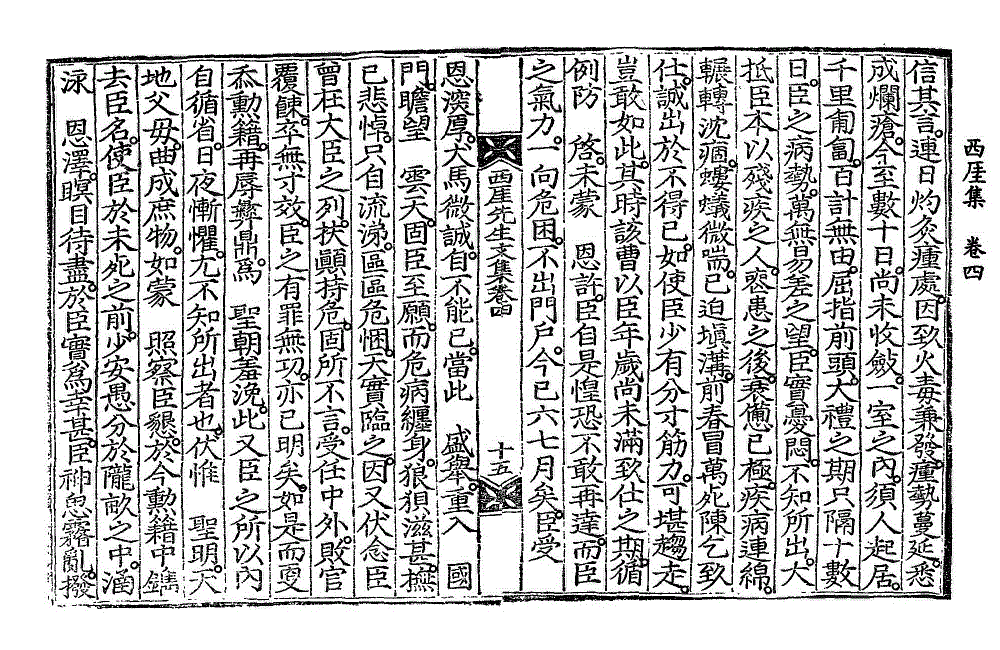 信其言。连日灼灸尰处。因致火毒兼发。尰势蔓延。悉成烂疮。今至数十日。尚未收敛。一室之内。须人起居。千里匍匐。百计无由。屈指前头。大礼之期只隔十数日。臣之病势。万无易差之望。臣实忧闷。不知所出。大抵臣本以残疾之人。丧患之后。衰惫已极。疾病连绵。辗转沈痼。蝼蚁微喘。已迫填沟。前春冒万死陈乞致仕。诚出于不得已。如使臣少有分寸筋力。可堪趋走。岂敢如此。其时该曹以臣年岁尚未满致仕之期。循例防 启。未蒙 恩许。臣自是惶恐不敢再达。而臣之气力。一向危困。不出门户。今已六七月矣。臣受 恩深厚。犬马微诚。自不能已。当此 盛举。重入 国门。瞻望 云天。固臣至愿。而危病缠身。狼狈滋甚。抚己悲悼。只自流涕。区区危悃。天实临之。因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扶颠持危。固所不言。受任中外。败官覆餗。卒无寸效。臣之有罪无功。亦已明矣。如是而更忝勋籍。再辱彝鼎。为 圣朝羞浼。此又臣之所以内自循省。日夜惭惧。尤不知所出者也。伏惟 圣明。天地父母。曲成庶物。如蒙 照察臣恳。于今勋籍中镌去臣名。使臣于未死之前。少安愚分于陇亩之中。涵泳 恩泽。暝目待尽。于臣实为幸甚。臣神思霿乱。拨
信其言。连日灼灸尰处。因致火毒兼发。尰势蔓延。悉成烂疮。今至数十日。尚未收敛。一室之内。须人起居。千里匍匐。百计无由。屈指前头。大礼之期只隔十数日。臣之病势。万无易差之望。臣实忧闷。不知所出。大抵臣本以残疾之人。丧患之后。衰惫已极。疾病连绵。辗转沈痼。蝼蚁微喘。已迫填沟。前春冒万死陈乞致仕。诚出于不得已。如使臣少有分寸筋力。可堪趋走。岂敢如此。其时该曹以臣年岁尚未满致仕之期。循例防 启。未蒙 恩许。臣自是惶恐不敢再达。而臣之气力。一向危困。不出门户。今已六七月矣。臣受 恩深厚。犬马微诚。自不能已。当此 盛举。重入 国门。瞻望 云天。固臣至愿。而危病缠身。狼狈滋甚。抚己悲悼。只自流涕。区区危悃。天实临之。因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扶颠持危。固所不言。受任中外。败官覆餗。卒无寸效。臣之有罪无功。亦已明矣。如是而更忝勋籍。再辱彝鼎。为 圣朝羞浼。此又臣之所以内自循省。日夜惭惧。尤不知所出者也。伏惟 圣明。天地父母。曲成庶物。如蒙 照察臣恳。于今勋籍中镌去臣名。使臣于未死之前。少安愚分于陇亩之中。涵泳 恩泽。暝目待尽。于臣实为幸甚。臣神思霿乱。拨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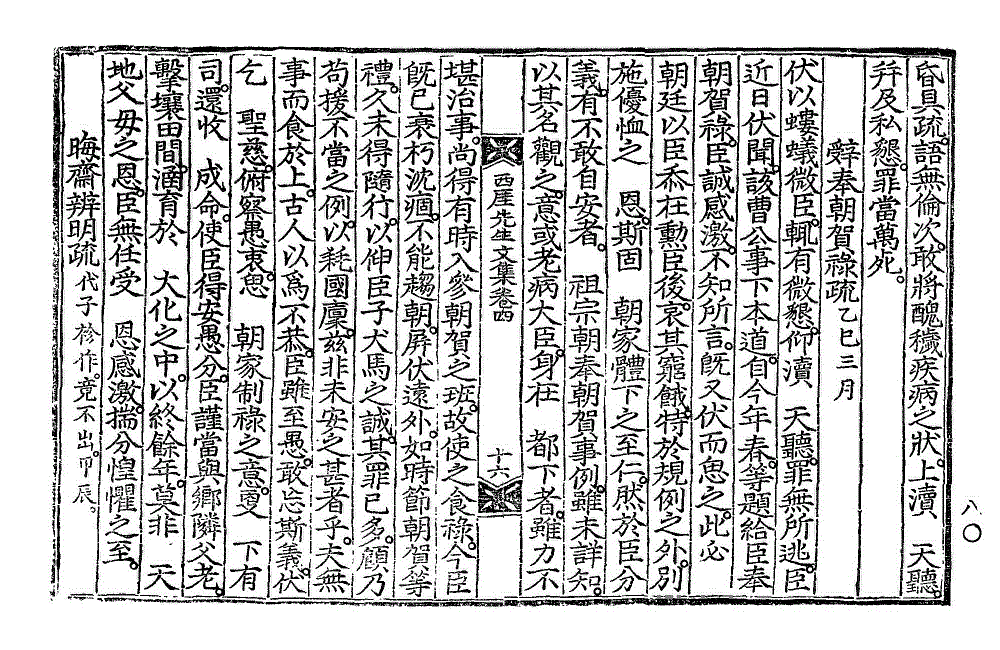 昏具疏。语无伦次。敢将丑秽疾病之状。上渎 天听。并及私恳。罪当万死。
昏具疏。语无伦次。敢将丑秽疾病之状。上渎 天听。并及私恳。罪当万死。辞奉朝贺禄疏(乙巳三月)
伏以蝼蚁微臣。辄有微恳。仰渎 天听。罪无所逃。臣近日伏闻。该曹公事下本道。自今年春。等题给臣奉朝贺禄。臣诚感激。不知所言。既又伏而思之。此必 朝廷以臣忝在勋臣后。哀其穷饿。特于规例之外。别施优恤之 恩。斯固 朝家体下之至仁。然于臣分义。有不敢自安者。 祖宗朝奉朝贺事例。虽未详知。以其名观之。意或老病大臣。身在 都下者。虽力不堪治事。尚得有时入参朝贺之班。故使之食禄。今臣既已衰朽沈痼。不能趋朝。屏伏远外。如时节朝贺等礼。久未得随行。以伸臣子犬马之诚。其罪已多。顾乃苟援不当之例。以耗国廪。玆非未安之甚者乎。夫无事而食于上。古人以为不恭。臣虽至愚。敢忘斯义。伏乞 圣慈。俯察愚衷。思 朝家制禄之意。更 下有司。还收 成命。使臣得安愚分。臣谨当与乡邻父老。击壤田间。涵育于 大化之中。以终馀年。莫非 天地父母之恩。臣无任受 恩感激。揣分惶惧之至。
晦斋辨明疏(代子袗作。竟不出○甲辰。)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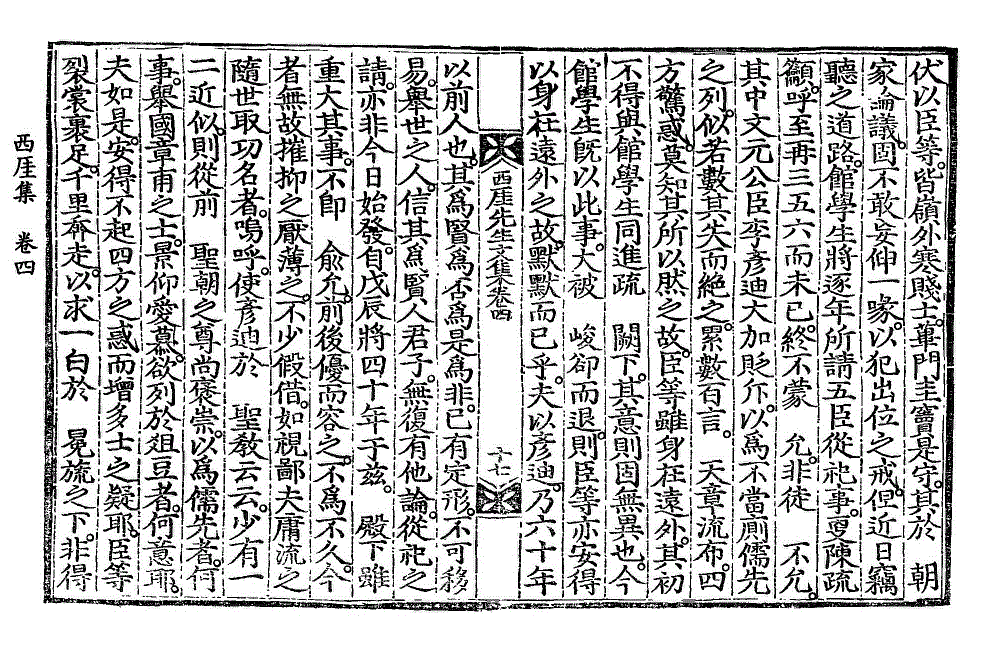 伏以臣等。皆岭外寒贱士。荜门圭窦是守。其于 朝家论议。固不敢妄伸一喙。以犯出位之戒。但近日窃听之道路。馆学生将逐年所请五臣从祀事。更陈疏吁。呼至再三五六而未已。终不蒙 允。非徒 不允。其中文元公臣李彦迪大加贬斥。以为不当厕儒先之列。似若数其失而绝之。累数百言。 天章流布。四方惊惑。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臣等虽身在远外。其初不得与馆学生同进疏 阙下。其意则固无异也。今馆学生既以此事。大被 峻却而退。则臣等亦安得以身在远外之故。默默而已乎。夫以彦迪。乃六十年以前人也。其为贤为否为是为非。已有定形。不可移易。举世之人。信其为贤人君子。无复有他论。从祀之请。亦非今日始发。自戊辰将四十年于玆。 殿下虽重大其事。不即 俞允。前后优而容之。不为不久。今者无故摧抑之厌薄之。不少假借。如视鄙夫庸流之随世取功名者。呜呼。使彦迪于 圣教云云。少有一二近似。则从前 圣朝之尊尚褒崇。以为儒先者。何事。举国章甫之士。景仰爱慕。欲列于俎豆者。何意耶。夫如是。安得不起四方之惑而增多士之疑耶。臣等裂裳里足。千里奔走。以求一白于 冕旒之下。非得
伏以臣等。皆岭外寒贱士。荜门圭窦是守。其于 朝家论议。固不敢妄伸一喙。以犯出位之戒。但近日窃听之道路。馆学生将逐年所请五臣从祀事。更陈疏吁。呼至再三五六而未已。终不蒙 允。非徒 不允。其中文元公臣李彦迪大加贬斥。以为不当厕儒先之列。似若数其失而绝之。累数百言。 天章流布。四方惊惑。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臣等虽身在远外。其初不得与馆学生同进疏 阙下。其意则固无异也。今馆学生既以此事。大被 峻却而退。则臣等亦安得以身在远外之故。默默而已乎。夫以彦迪。乃六十年以前人也。其为贤为否为是为非。已有定形。不可移易。举世之人。信其为贤人君子。无复有他论。从祀之请。亦非今日始发。自戊辰将四十年于玆。 殿下虽重大其事。不即 俞允。前后优而容之。不为不久。今者无故摧抑之厌薄之。不少假借。如视鄙夫庸流之随世取功名者。呜呼。使彦迪于 圣教云云。少有一二近似。则从前 圣朝之尊尚褒崇。以为儒先者。何事。举国章甫之士。景仰爱慕。欲列于俎豆者。何意耶。夫如是。安得不起四方之惑而增多士之疑耶。臣等裂裳里足。千里奔走。以求一白于 冕旒之下。非得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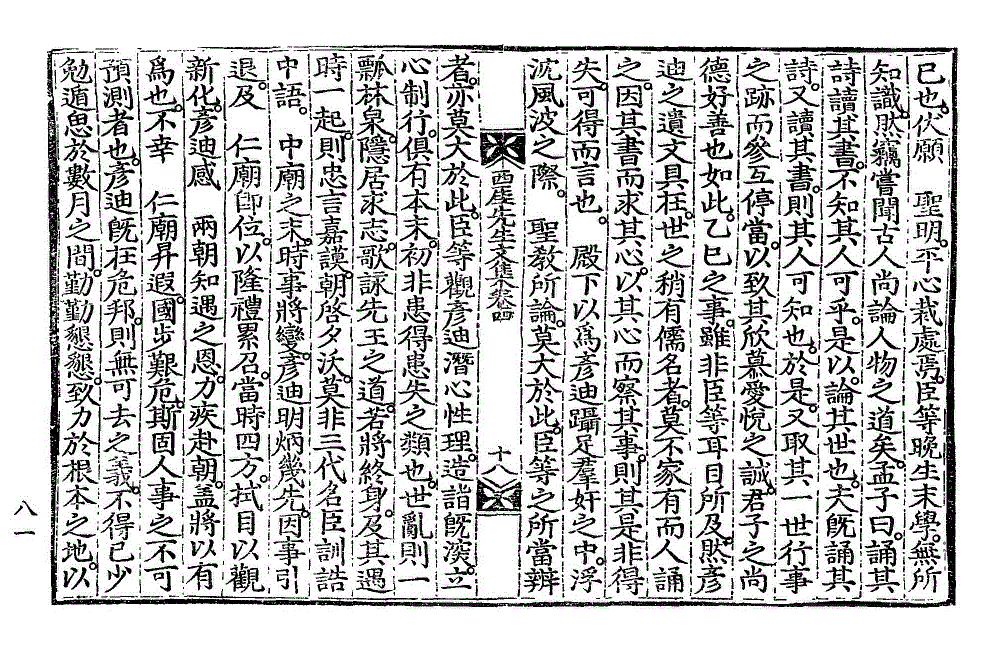 已也。伏愿 圣明。平心裁处焉。臣等晚生末学。无所知识。然窃尝闻古人尚论人物之道矣。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夫既诵其诗。又读其书。则其人可知也。于是。又取其一世行事之迹而参互停当。以致其欣慕爱悦之诚。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乙巳之事。虽非臣等耳目所及。然彦迪之遗文具在。世之稍有儒名者。莫不家有而人诵之。因其书而求其心。以其心而察其事。则其是非得失。可得而言也。 殿下以为彦迪蹑足群奸之中。浮沈风波之际。 圣教所论。莫大于此。臣等之所当辨者。亦莫大于此。臣等观彦迪潜心性理。造诣既深。立心制行。俱有本末。初非患得患失之类也。世乱则一瓢林泉。隐居求志。歌咏先王之道。若将终身。及其遇时一起。则忠言嘉谟。朝启夕沃。莫非三代名臣训诰中语。 中庙之末。时事将变。彦迪明炳几先。因事引退。及 仁庙即位。以隆礼累召。当时四方。拭目以观新化。彦迪感 两朝知遇之恩。力疾赴朝。盖将以有为也。不幸 仁庙升遐。国步艰危。斯固人事之不可预测者也。彦迪既在危邦。则无可去之义。不得已少勉遁思于数月之间。勤勤恳恳。致力于根本之地。以
已也。伏愿 圣明。平心裁处焉。臣等晚生末学。无所知识。然窃尝闻古人尚论人物之道矣。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夫既诵其诗。又读其书。则其人可知也。于是。又取其一世行事之迹而参互停当。以致其欣慕爱悦之诚。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乙巳之事。虽非臣等耳目所及。然彦迪之遗文具在。世之稍有儒名者。莫不家有而人诵之。因其书而求其心。以其心而察其事。则其是非得失。可得而言也。 殿下以为彦迪蹑足群奸之中。浮沈风波之际。 圣教所论。莫大于此。臣等之所当辨者。亦莫大于此。臣等观彦迪潜心性理。造诣既深。立心制行。俱有本末。初非患得患失之类也。世乱则一瓢林泉。隐居求志。歌咏先王之道。若将终身。及其遇时一起。则忠言嘉谟。朝启夕沃。莫非三代名臣训诰中语。 中庙之末。时事将变。彦迪明炳几先。因事引退。及 仁庙即位。以隆礼累召。当时四方。拭目以观新化。彦迪感 两朝知遇之恩。力疾赴朝。盖将以有为也。不幸 仁庙升遐。国步艰危。斯固人事之不可预测者也。彦迪既在危邦。则无可去之义。不得已少勉遁思于数月之间。勤勤恳恳。致力于根本之地。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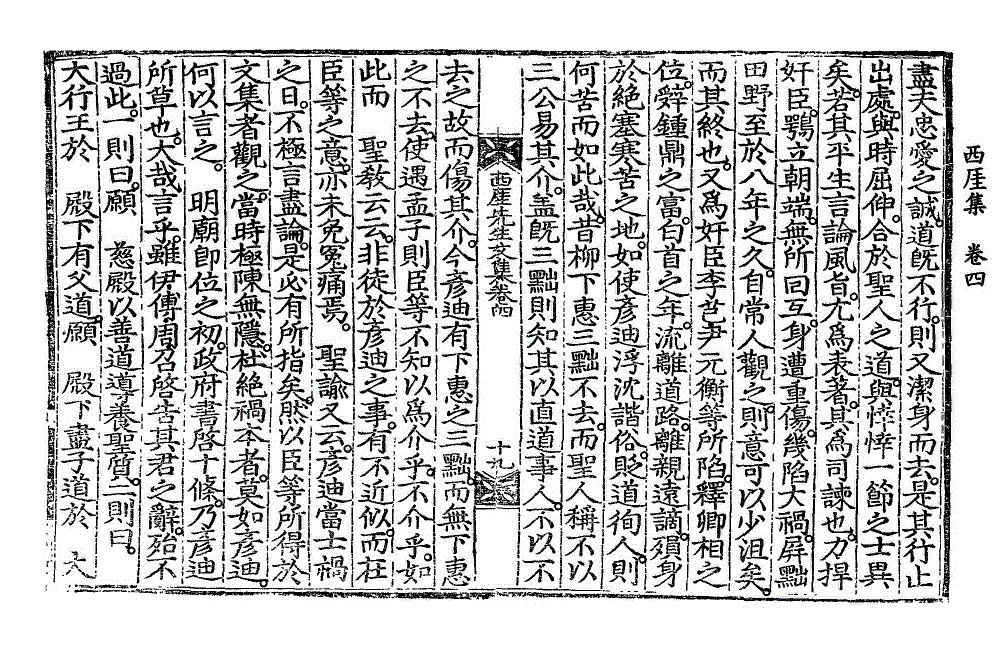 尽夫忠爱之诚。道既不行。则又洁身而去。是其行止出处。与时屈伸。合于圣人之道。与悻悻一节之士异矣。若其平生言论风旨。尤为表著。其为司谏也。力捍奸臣。鹗立朝端。无所回互。身遭重伤。几陷大祸。屏黜田野至于八年之久。自常人观之。则意可以少沮矣。而其终也。又为奸臣李芑,尹元衡等所陷。释卿相之位。辞钟鼎之富。白首之年。流离道路。离亲远谪。殒身于绝塞寒苦之地。如使彦迪浮沈谐俗。贬道徇人。则何苦而如此哉。昔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圣人称不以三公易其介。盖既三黜则知其以直道事人。不以不去之故而伤其介。今彦迪有下惠之三黜。而无下惠之不去。使遇孟子则臣等不知以为介乎。不介乎。如此而 圣教云云。非徒于彦迪之事。有不近似。而在臣等之意。亦未免冤痛焉。 圣谕又云。彦迪当士祸之日。不极言尽论。是必有所指矣。然以臣等所得于文集者观之。当时极陈无隐。杜绝祸本者。莫如彦迪。何以言之。 明庙即位之初。政府书启十条。乃彦迪所草也。大哉言乎。虽伊,傅,周,召启告其君之辞。殆不过此。一则曰。愿 慈殿以善道导养圣质。二则曰。 大行王于 殿下有父道。愿 殿下尽子道于 大
尽夫忠爱之诚。道既不行。则又洁身而去。是其行止出处。与时屈伸。合于圣人之道。与悻悻一节之士异矣。若其平生言论风旨。尤为表著。其为司谏也。力捍奸臣。鹗立朝端。无所回互。身遭重伤。几陷大祸。屏黜田野至于八年之久。自常人观之。则意可以少沮矣。而其终也。又为奸臣李芑,尹元衡等所陷。释卿相之位。辞钟鼎之富。白首之年。流离道路。离亲远谪。殒身于绝塞寒苦之地。如使彦迪浮沈谐俗。贬道徇人。则何苦而如此哉。昔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圣人称不以三公易其介。盖既三黜则知其以直道事人。不以不去之故而伤其介。今彦迪有下惠之三黜。而无下惠之不去。使遇孟子则臣等不知以为介乎。不介乎。如此而 圣教云云。非徒于彦迪之事。有不近似。而在臣等之意。亦未免冤痛焉。 圣谕又云。彦迪当士祸之日。不极言尽论。是必有所指矣。然以臣等所得于文集者观之。当时极陈无隐。杜绝祸本者。莫如彦迪。何以言之。 明庙即位之初。政府书启十条。乃彦迪所草也。大哉言乎。虽伊,傅,周,召启告其君之辞。殆不过此。一则曰。愿 慈殿以善道导养圣质。二则曰。 大行王于 殿下有父道。愿 殿下尽子道于 大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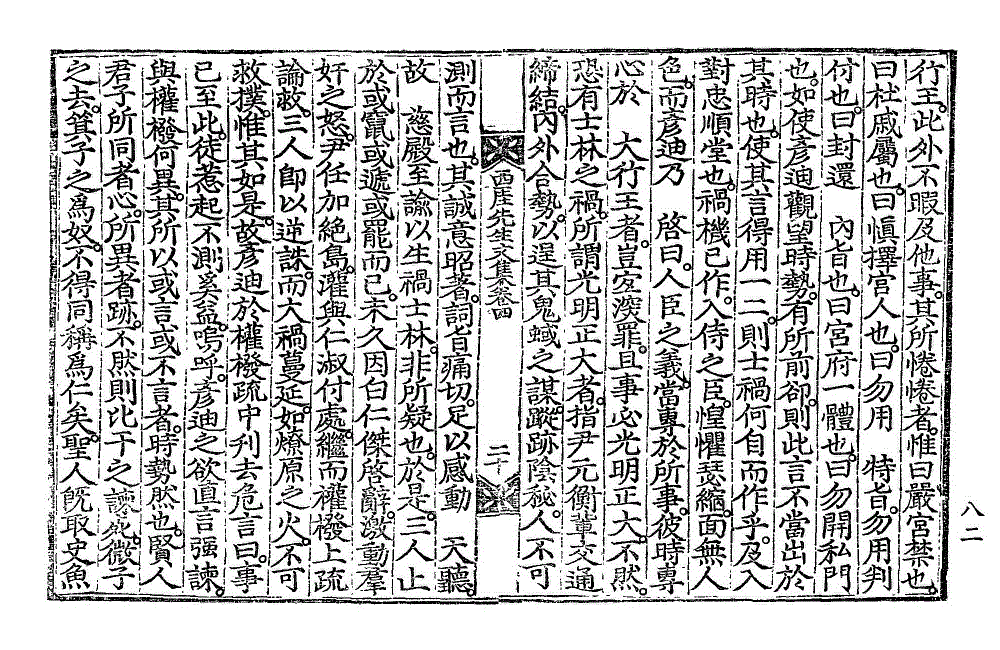 行王。此外不暇及他事。其所惓惓者。惟曰严宫禁也。曰杜戚属也。曰慎择宫人也。曰勿用 特旨。勿用判付也。曰封还 内旨也。曰宫府一体也。曰勿开私门也。如使彦迪观望时势。有所前却。则此言不当出于其时也。使其言得用一二。则士祸何自而作乎。及入对忠顺堂也。祸机已作。入侍之臣。惶惧瑟缩。面无人色。而彦迪乃 启曰。人臣之义。当专于所事。彼时专心于 大行王者。岂宜深罪。且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祸。所谓光明正大者。指尹元衡辈交通缔结。内外合势。以逞其鬼蜮之谋。踪迹阴秘。人不可测而言也。其诚意昭著。词旨痛切。足以感动 天听。故 慈殿至谕以生祸士林。非所疑也。于是。三人止于或窜或递或罢而已。未久因白仁杰启辞。激动群奸之怒。尹任加绝岛。灌与仁淑付处。继而权橃上疏论救。三人即以逆诛。而大祸蔓延。如燎原之火。不可救扑。惟其如是。故彦迪于权橃疏中刊去危言曰。事已至此。徒惹起不测奚益。呜呼。彦迪之欲直言强谏。与权橃何异。其所以或言或不言者。时势然也。贤人君子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不然则比干之谏死。微子之去。箕子之为奴。不得同称为仁矣。圣人既取史鱼
行王。此外不暇及他事。其所惓惓者。惟曰严宫禁也。曰杜戚属也。曰慎择宫人也。曰勿用 特旨。勿用判付也。曰封还 内旨也。曰宫府一体也。曰勿开私门也。如使彦迪观望时势。有所前却。则此言不当出于其时也。使其言得用一二。则士祸何自而作乎。及入对忠顺堂也。祸机已作。入侍之臣。惶惧瑟缩。面无人色。而彦迪乃 启曰。人臣之义。当专于所事。彼时专心于 大行王者。岂宜深罪。且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祸。所谓光明正大者。指尹元衡辈交通缔结。内外合势。以逞其鬼蜮之谋。踪迹阴秘。人不可测而言也。其诚意昭著。词旨痛切。足以感动 天听。故 慈殿至谕以生祸士林。非所疑也。于是。三人止于或窜或递或罢而已。未久因白仁杰启辞。激动群奸之怒。尹任加绝岛。灌与仁淑付处。继而权橃上疏论救。三人即以逆诛。而大祸蔓延。如燎原之火。不可救扑。惟其如是。故彦迪于权橃疏中刊去危言曰。事已至此。徒惹起不测奚益。呜呼。彦迪之欲直言强谏。与权橃何异。其所以或言或不言者。时势然也。贤人君子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不然则比干之谏死。微子之去。箕子之为奴。不得同称为仁矣。圣人既取史鱼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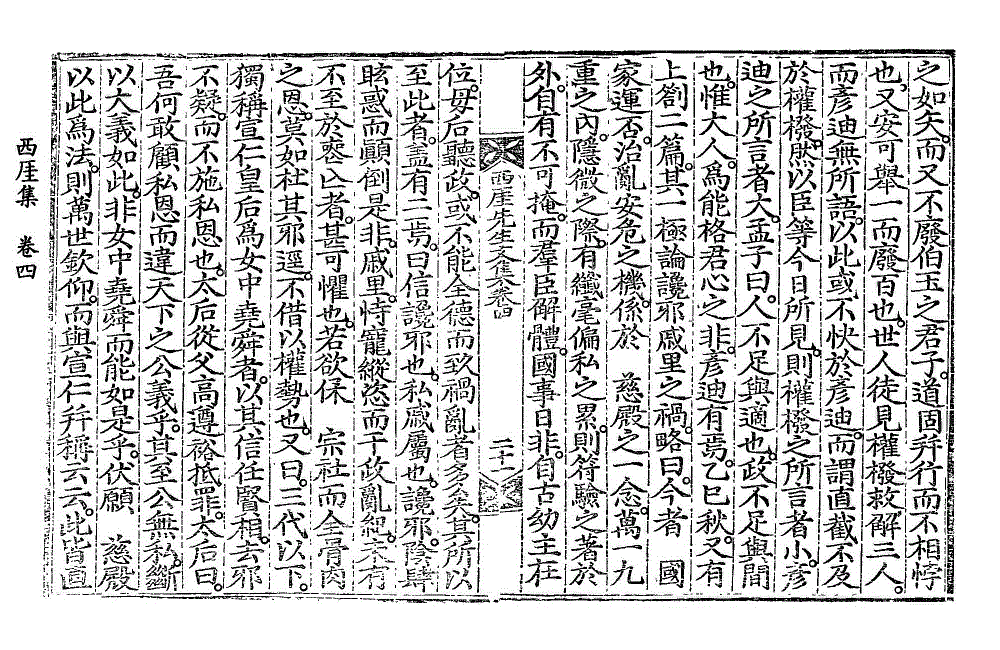 之如矢。而又不废伯玉之君子。道固并行而不相悖也。又安可举一而废百也。世人徒见权橃救解三人。而彦迪无所语。以此或不快于彦迪。而谓直截不及于权橃。然以臣等今日所见。则权橃之所言者小。彦迪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彦迪有焉。乙巳秋。又有上劄二篇。其一极论谗邪戚里之祸。略曰。今者 国家运否。治乱安危之机。系于 慈殿之一念。万一九重之内。隐微之际。有纤毫偏私之累。则符验之著于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体。国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听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祸乱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盖有二焉。曰信谗邪也。私戚属也。谗邪。阴肆眩惑而颠倒是非。戚里。恃宠纵恣而干政乱纪。未有不至于丧亡者。甚可惧也。若欲保 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径。不借以权势也。又曰。三代以下。独称宣仁皇后为女中尧舜者。以其信任贤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从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之公义乎。其至公无私。断以大义如此。非女中尧舜而能如是乎。伏愿 慈殿以此为法。则万世钦仰。而与宣仁并称云云。此皆直
之如矢。而又不废伯玉之君子。道固并行而不相悖也。又安可举一而废百也。世人徒见权橃救解三人。而彦迪无所语。以此或不快于彦迪。而谓直截不及于权橃。然以臣等今日所见。则权橃之所言者小。彦迪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彦迪有焉。乙巳秋。又有上劄二篇。其一极论谗邪戚里之祸。略曰。今者 国家运否。治乱安危之机。系于 慈殿之一念。万一九重之内。隐微之际。有纤毫偏私之累。则符验之著于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体。国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听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祸乱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盖有二焉。曰信谗邪也。私戚属也。谗邪。阴肆眩惑而颠倒是非。戚里。恃宠纵恣而干政乱纪。未有不至于丧亡者。甚可惧也。若欲保 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径。不借以权势也。又曰。三代以下。独称宣仁皇后为女中尧舜者。以其信任贤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从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之公义乎。其至公无私。断以大义如此。非女中尧舜而能如是乎。伏愿 慈殿以此为法。则万世钦仰。而与宣仁并称云云。此皆直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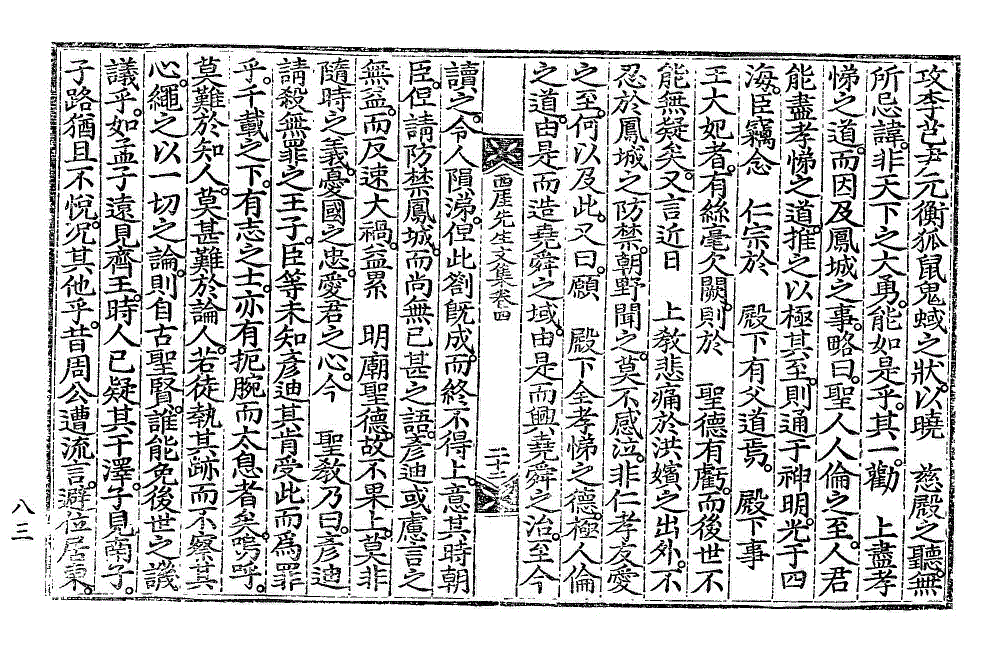 攻李芑,尹元衡狐鼠鬼蜮之状。以晓 慈殿之听。无所忌讳。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劝 上尽孝悌之道。而因及凤城之事。略曰。圣人人伦之至。人君能尽孝悌之道。推之以极其至。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臣窃念 仁宗于 殿下有父道焉。 殿下事 王大妃者。有丝毫欠阙。则于 圣德有亏。而后世不能无疑矣。又言近日 上教悲痛于洪嫔之出外。不忍于凤城之防禁。朝野闻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爱之至。何以及此。又曰。愿 殿下全孝悌之德。极人伦之道。由是而造尧舜之域。由是而兴尧舜之治。至今读之。令人陨涕。但此劄既成。而终不得上。意其时朝臣。但请防禁凤城。而尚无已甚之语。彦迪或虑言之无益。而反速大祸。益累 明庙圣德。故不果上。莫非随时之义。忧国之忠。爱君之心。今 圣教乃曰。彦迪请杀无罪之王子。臣等未知彦迪其肯受此而为罪乎。千载之下。有志之士。亦有扼腕而太息者矣。呜呼。莫难于知人。莫甚难于论人。若徒执其迹而不察其心。绳之以一切之论。则自古圣贤。谁能免后世之讥议乎。如孟子远见齐王。时人已疑其干泽。子见南子。子路犹且不悦。况其他乎。昔周公遭流言。避位居东。
攻李芑,尹元衡狐鼠鬼蜮之状。以晓 慈殿之听。无所忌讳。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劝 上尽孝悌之道。而因及凤城之事。略曰。圣人人伦之至。人君能尽孝悌之道。推之以极其至。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臣窃念 仁宗于 殿下有父道焉。 殿下事 王大妃者。有丝毫欠阙。则于 圣德有亏。而后世不能无疑矣。又言近日 上教悲痛于洪嫔之出外。不忍于凤城之防禁。朝野闻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爱之至。何以及此。又曰。愿 殿下全孝悌之德。极人伦之道。由是而造尧舜之域。由是而兴尧舜之治。至今读之。令人陨涕。但此劄既成。而终不得上。意其时朝臣。但请防禁凤城。而尚无已甚之语。彦迪或虑言之无益。而反速大祸。益累 明庙圣德。故不果上。莫非随时之义。忧国之忠。爱君之心。今 圣教乃曰。彦迪请杀无罪之王子。臣等未知彦迪其肯受此而为罪乎。千载之下。有志之士。亦有扼腕而太息者矣。呜呼。莫难于知人。莫甚难于论人。若徒执其迹而不察其心。绳之以一切之论。则自古圣贤。谁能免后世之讥议乎。如孟子远见齐王。时人已疑其干泽。子见南子。子路犹且不悦。况其他乎。昔周公遭流言。避位居东。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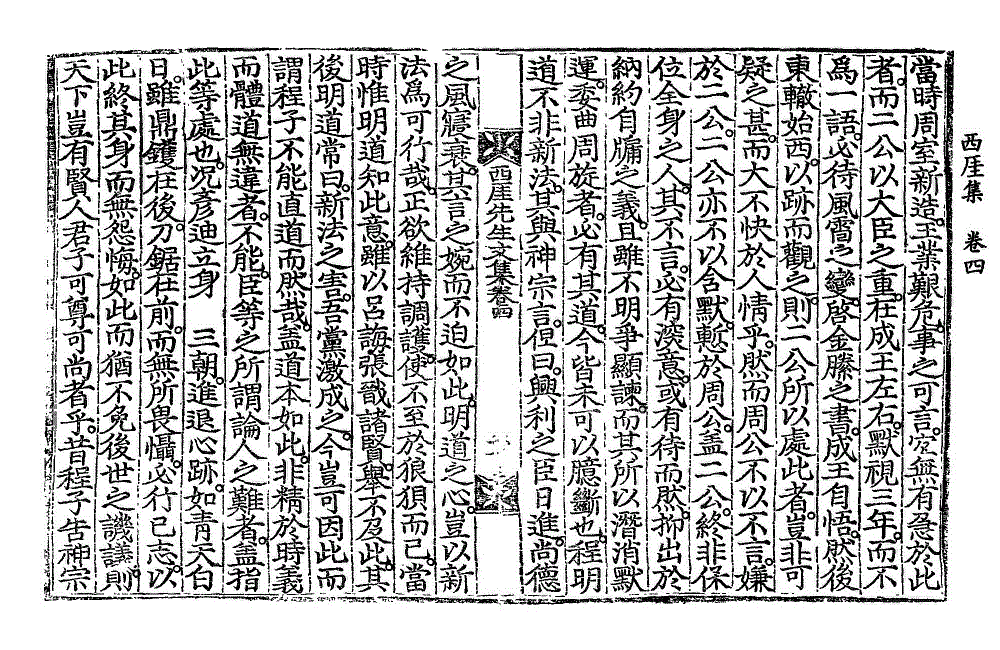 当时周室新造。王业艰危。事之可言。宜无有急于此者。而二公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默视三年。而不为一语。必待风雷之变。启金縢之书。成王自悟。然后东辙始西。以迹而观之。则二公所以处此者。岂非可疑之甚。而大不快于人情乎。然而周公不以不言。嫌于二公。二公亦不以含默。惭于周公。盖二公。终非保位全身之人。其不言。必有深意。或有待而然。抑出于纳约自牖之义。且虽不明争显谏。而其所以潜消默运。委曲周旋者。必有其道。今皆未可以臆断也。程明道不非新法。其与神宗言。但曰。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其言之婉而不迫如此。明道之心。岂以新法为可行哉。正欲维持调护。使不至于狼狈而已。当时惟明道知此意。虽以吕诲,张戬诸贤。举不及此。其后明道常曰。新法之害。吾党激成之。今岂可因此而谓程子不能直道而然哉。盖道本如此。非精于时义而体道无违者。不能。臣等之所谓论人之难者。盖指此等处也。况彦迪立身 三朝。进退心迹。如青天白日。虽鼎镬在后。刀锯在前。而无所畏慑。必行己志。以此终其身而无怨悔。如此而犹不免后世之讥议。则天下岂有贤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昔程子告神宗
当时周室新造。王业艰危。事之可言。宜无有急于此者。而二公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默视三年。而不为一语。必待风雷之变。启金縢之书。成王自悟。然后东辙始西。以迹而观之。则二公所以处此者。岂非可疑之甚。而大不快于人情乎。然而周公不以不言。嫌于二公。二公亦不以含默。惭于周公。盖二公。终非保位全身之人。其不言。必有深意。或有待而然。抑出于纳约自牖之义。且虽不明争显谏。而其所以潜消默运。委曲周旋者。必有其道。今皆未可以臆断也。程明道不非新法。其与神宗言。但曰。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其言之婉而不迫如此。明道之心。岂以新法为可行哉。正欲维持调护。使不至于狼狈而已。当时惟明道知此意。虽以吕诲,张戬诸贤。举不及此。其后明道常曰。新法之害。吾党激成之。今岂可因此而谓程子不能直道而然哉。盖道本如此。非精于时义而体道无违者。不能。臣等之所谓论人之难者。盖指此等处也。况彦迪立身 三朝。进退心迹。如青天白日。虽鼎镬在后。刀锯在前。而无所畏慑。必行己志。以此终其身而无怨悔。如此而犹不免后世之讥议。则天下岂有贤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昔程子告神宗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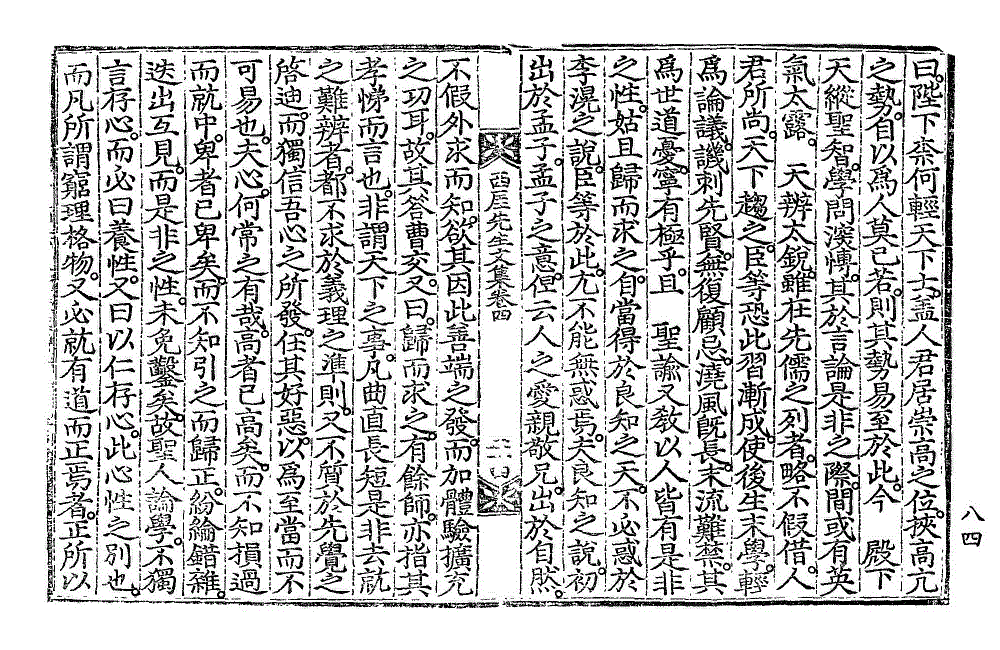 曰。陛下柰何轻天下士。盖人君居崇高之位。挟高亢之势。自以为人莫己若。则其势易至于此。今 殿下天纵圣智。学问深博。其于言论是非之际。间或有英气太露。 天辨太锐。虽在先儒之列者。略不假借。人君所尚。天下趋之。臣等恐此习渐成。使后生末学。轻为论议。讥刺先贤。无复顾忌。浇风既长。末流难禁。其为世道忧。宁有极乎。且 圣谕又教以人皆有是非之性。姑且归而求之。自当得于良知之天。不必惑于李滉之说。臣等于此。尤不能无惑焉。夫良知之说。初出于孟子。孟子之意。但云人之爱亲敬兄。出于自然。不假外求而知。欲其因此善端之发。而加体验扩充之功耳。故其答曹交。又曰。归而求之。有馀师。亦指其孝悌而言也。非谓天下之事。凡曲直长短是非去就之难辨者。都不求于义理之准则。又不质于先觉之启迪。而独信吾心之所发。任其好恶。以为至当而不可易也。夫心。何常之有哉。高者已高矣。而不知损过而就中。卑者已卑矣。而不知引之而归正。纷纶错杂。迭出互见。而是非之性。未免凿矣。故圣人论学。不独言存心。而必曰养性。又曰以仁存心。此心性之别也。而凡所谓穷理格物。又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正所以
曰。陛下柰何轻天下士。盖人君居崇高之位。挟高亢之势。自以为人莫己若。则其势易至于此。今 殿下天纵圣智。学问深博。其于言论是非之际。间或有英气太露。 天辨太锐。虽在先儒之列者。略不假借。人君所尚。天下趋之。臣等恐此习渐成。使后生末学。轻为论议。讥刺先贤。无复顾忌。浇风既长。末流难禁。其为世道忧。宁有极乎。且 圣谕又教以人皆有是非之性。姑且归而求之。自当得于良知之天。不必惑于李滉之说。臣等于此。尤不能无惑焉。夫良知之说。初出于孟子。孟子之意。但云人之爱亲敬兄。出于自然。不假外求而知。欲其因此善端之发。而加体验扩充之功耳。故其答曹交。又曰。归而求之。有馀师。亦指其孝悌而言也。非谓天下之事。凡曲直长短是非去就之难辨者。都不求于义理之准则。又不质于先觉之启迪。而独信吾心之所发。任其好恶。以为至当而不可易也。夫心。何常之有哉。高者已高矣。而不知损过而就中。卑者已卑矣。而不知引之而归正。纷纶错杂。迭出互见。而是非之性。未免凿矣。故圣人论学。不独言存心。而必曰养性。又曰以仁存心。此心性之别也。而凡所谓穷理格物。又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正所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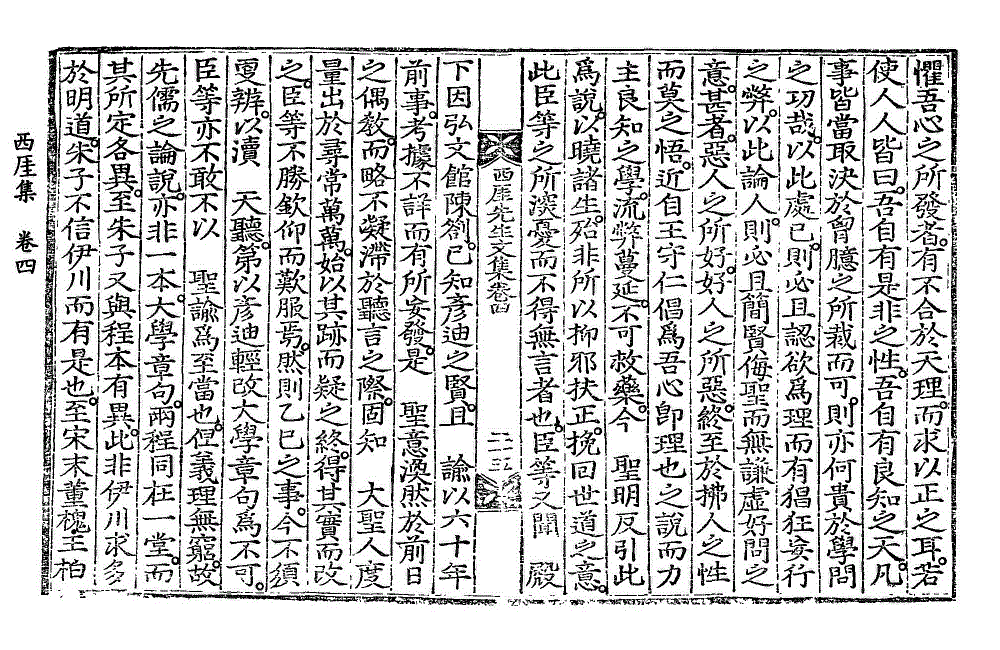 惧吾心之所发者。有不合于天理。而求以正之耳。若使人人皆曰。吾自有是非之性。吾自有良知之天。凡事皆当取决于胸臆之所裁而可。则亦何贵于学问之功哉。以此处己。则必且认欲为理而有猖狂妄行之弊。以此论人。则必且简贤侮圣而无谦虚好问之意。甚者。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终至于拂人之性而莫之悟。近自王守仁倡为吾心即理也之说而力主良知之学。流弊蔓延。不可救药。今 圣明反引此为说。以晓诸生。殆非所以抑邪扶正。挽回世道之意。此臣等之所深忧而不得无言者也。臣等又闻 殿下因弘文馆陈劄。已知彦迪之贤。且 谕以六十年前事。考据不详而有所妄发。是 圣意涣然于前日之偶教。而略不凝滞于听言之际。固知 大圣人度量出于寻常万万。始以其迹而疑之终。得其实而改之。臣等不胜钦仰而叹服焉。然则乙巳之事。今不须更辨。以渎 天听。第以彦迪轻改大学章句为不可。臣等亦不敢不以 圣谕为至当也。但义理无穷。故先儒之论说。亦非一本。大学章句。两程同在一堂。而其所定各异。至朱子又与程本有异。此非伊川求多于明道。朱子不信伊川而有是也。至宋末董槐,王柏
惧吾心之所发者。有不合于天理。而求以正之耳。若使人人皆曰。吾自有是非之性。吾自有良知之天。凡事皆当取决于胸臆之所裁而可。则亦何贵于学问之功哉。以此处己。则必且认欲为理而有猖狂妄行之弊。以此论人。则必且简贤侮圣而无谦虚好问之意。甚者。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终至于拂人之性而莫之悟。近自王守仁倡为吾心即理也之说而力主良知之学。流弊蔓延。不可救药。今 圣明反引此为说。以晓诸生。殆非所以抑邪扶正。挽回世道之意。此臣等之所深忧而不得无言者也。臣等又闻 殿下因弘文馆陈劄。已知彦迪之贤。且 谕以六十年前事。考据不详而有所妄发。是 圣意涣然于前日之偶教。而略不凝滞于听言之际。固知 大圣人度量出于寻常万万。始以其迹而疑之终。得其实而改之。臣等不胜钦仰而叹服焉。然则乙巳之事。今不须更辨。以渎 天听。第以彦迪轻改大学章句为不可。臣等亦不敢不以 圣谕为至当也。但义理无穷。故先儒之论说。亦非一本。大学章句。两程同在一堂。而其所定各异。至朱子又与程本有异。此非伊川求多于明道。朱子不信伊川而有是也。至宋末董槐,王柏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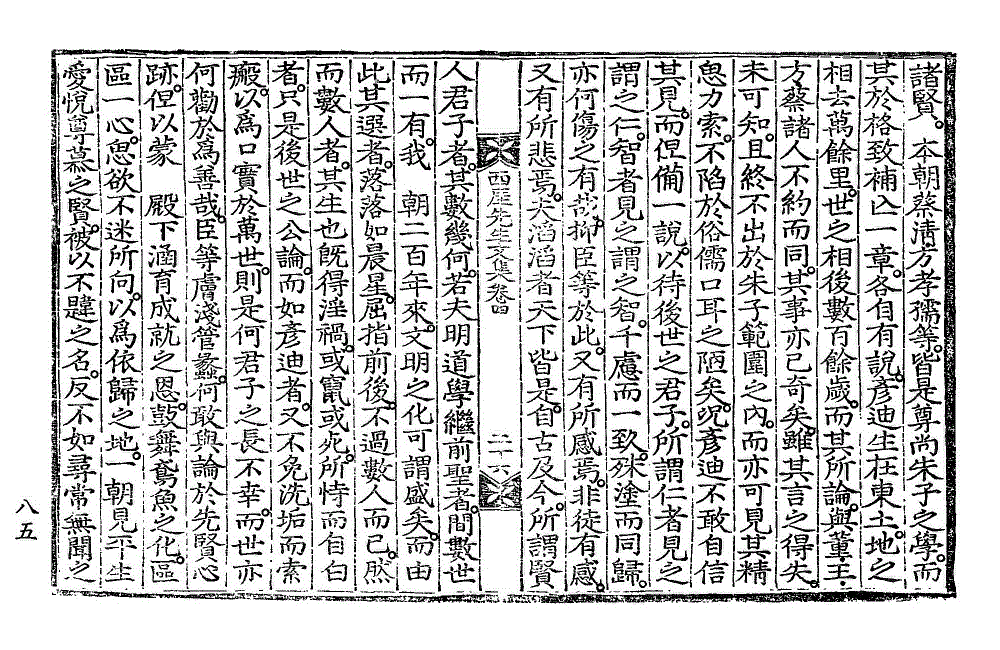 诸贤。 本朝蔡清,方孝孺等。皆是尊尚朱子之学。而其于格致补亡一章。各自有说。彦迪生在东土。地之相去万馀里。世之相后数百馀岁。而其所论。与董,王,方,蔡诸人不约而同。其事亦已奇矣。虽其言之得失。未可知。且终不出于朱子范围之内。而亦可见其精思力索。不陷于俗儒口耳之陋矣。况彦迪不敢自信其见。而但备一说。以待后世之君子。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千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亦何伤之有哉。抑臣等于此。又有所感焉。非徒有感。又有所悲焉。夫滔滔者天下皆是。自古及今。所谓贤人君子者。其数几何。若夫明道学继前圣者。间数世而一有。我 朝二百年来。文明之化可谓盛矣。而由此其选者。落落如晨星。屈指前后。不过数人而已。然而数人者。其生也既得淫祸。或窜或死。所恃而自白者。只是后世之公论。而如彦迪者。又不免洗垢而索瘢。以为口实于万世。则是何君子之长不幸。而世亦何劝于为善哉。臣等肤浅管蠡。何敢与论于先贤心迹。但以蒙 殿下涵育成就之恩。鼓舞鸢鱼之化。区区一心。思欲不迷所向。以为依归之地。一朝见平生爱悦尊慕之贤。被以不韪之名。反不如寻常无闻之
诸贤。 本朝蔡清,方孝孺等。皆是尊尚朱子之学。而其于格致补亡一章。各自有说。彦迪生在东土。地之相去万馀里。世之相后数百馀岁。而其所论。与董,王,方,蔡诸人不约而同。其事亦已奇矣。虽其言之得失。未可知。且终不出于朱子范围之内。而亦可见其精思力索。不陷于俗儒口耳之陋矣。况彦迪不敢自信其见。而但备一说。以待后世之君子。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千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亦何伤之有哉。抑臣等于此。又有所感焉。非徒有感。又有所悲焉。夫滔滔者天下皆是。自古及今。所谓贤人君子者。其数几何。若夫明道学继前圣者。间数世而一有。我 朝二百年来。文明之化可谓盛矣。而由此其选者。落落如晨星。屈指前后。不过数人而已。然而数人者。其生也既得淫祸。或窜或死。所恃而自白者。只是后世之公论。而如彦迪者。又不免洗垢而索瘢。以为口实于万世。则是何君子之长不幸。而世亦何劝于为善哉。臣等肤浅管蠡。何敢与论于先贤心迹。但以蒙 殿下涵育成就之恩。鼓舞鸢鱼之化。区区一心。思欲不迷所向。以为依归之地。一朝见平生爱悦尊慕之贤。被以不韪之名。反不如寻常无闻之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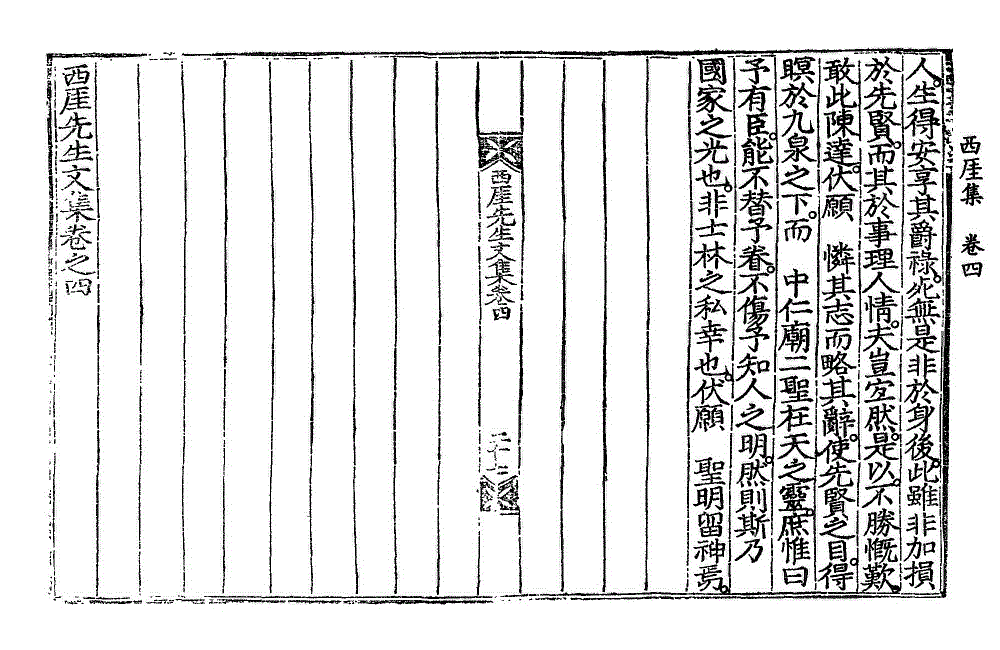 人。生得安享其爵禄。死无是非于身后。此虽非加损于先贤。而其于事理人情。夫岂宜然。是以。不胜慨叹。敢此陈达。伏愿 怜其志而略其辞。使先贤之目。得暝于九泉之下。而 中仁庙二圣在天之灵。庶惟曰予有臣。能不替予眷。不伤予知人之明。然则斯乃 国家之光也。非士林之私幸也。伏愿 圣明留神焉。
人。生得安享其爵禄。死无是非于身后。此虽非加损于先贤。而其于事理人情。夫岂宜然。是以。不胜慨叹。敢此陈达。伏愿 怜其志而略其辞。使先贤之目。得暝于九泉之下。而 中仁庙二圣在天之灵。庶惟曰予有臣。能不替予眷。不伤予知人之明。然则斯乃 国家之光也。非士林之私幸也。伏愿 圣明留神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