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跋
跋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1H 页
 题天地万物论后
题天地万物论后此篇。与性理彝训所载造化论相似。但篇首及中间添却数行文字。而其馀则大抵皆同。注亦不异。虽或字字有不同处。而此乃彼此誊写之误。全篇则若出于一人之手。诚可怪也。考其作者先后。则彝训乃豫章王孝友所著。而孝友即宋宝庆绍定间人。与魏鹤山黄勉斋同时。而此篇则王鲁斋所述也。鲁斋即何北山门人。而北山受业于勉斋门下。则其先后可见矣。若使鲁斋曾见孝友之作。不当攘取他作。掩为自家所述。若不见则一篇之立言命意。镕铸一范。无少违异。此又何也。无乃意思与古人暗合而然耶。且此篇乃成化间周颙所注。而弘治中吴文度跋其后。彝训则至正间易复初刊之。龙仁夫序之。蔡德懋发挥之。景泰中邹亮校正之。易也龙也蔡也。前于周吴几百年。邹亦数十年前矣。此篇既作于彝训行世之后。周注又出于彝训注释之后。而此篇既与彝训犁合。周注又与彝训之注若是其相似。此又可疑而不可知者也。姑识之以俟博闻。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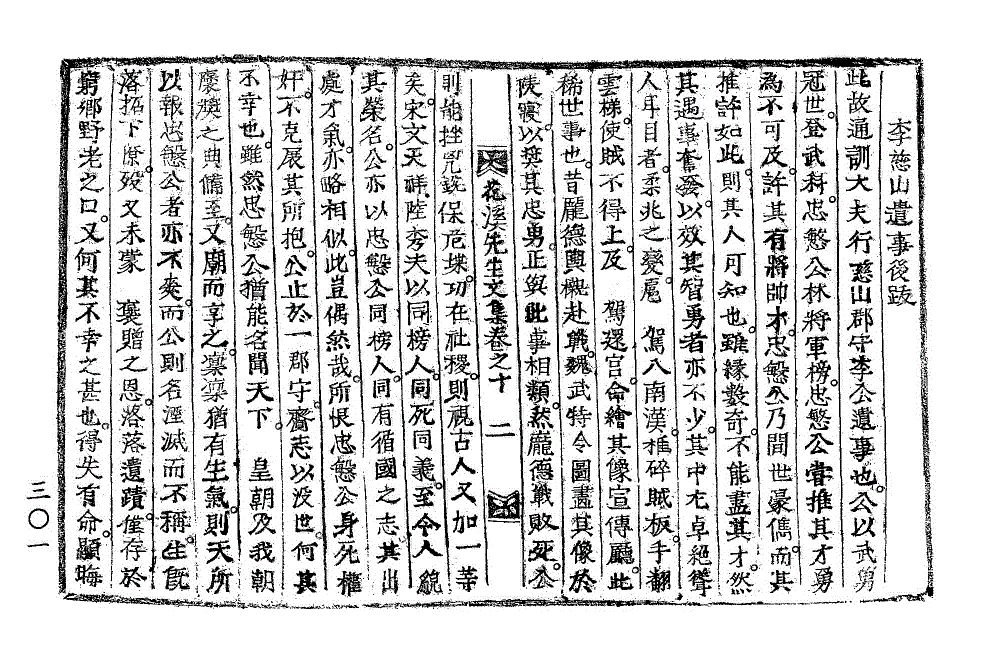 李慈山遗事后跋
李慈山遗事后跋此故通训大夫行慈山郡守李公遗事也。公以武勇冠世。登武科。忠慜公林将军榜。忠慜公尝推其才勇为不可及。许其有将帅才。忠慜公乃间世豪俊。而其推许如此。则其人可知也。虽缘数奇。不能尽其才。然其遇事奋发。以效其智勇者亦不少。其中尤卓绝耸人耳目者。柔兆之变。扈 驾入南汉。椎碎贼板。手翻云梯。使贼不得上。及 驾还宫。命绘其像宣传厅。此稀世事也。昔庞德舆榇赴战。魏武特令图画其像于陵寝。以奖其忠勇。正与此事相类。然庞德战败死。公则能挫凶锐保危堞。功在社稷。则视古人又加一等矣。宋文天祥,陆秀夫以同榜人。同死同义。至今人貌其荣名。公亦以忠慜公同榜人。同有循国之志。其出处才气。亦略相似。此岂偶然哉。所恨忠慜公身死权奸。不克展其所抱。公止于一郡守。赍志以没世。何其不幸也。虽然忠慜公犹能名闻天下。 皇朝及我朝褒奖之典备至。又庙而享之。凛凛犹有生气。则天所以报忠慜公者亦不爽。而公则名湮灭而不称。生既落拓下僚。殁又未蒙 褒赠之恩。落落遗迹。仅存于穷乡野老之口。又何其不幸之甚也。得失有命。显晦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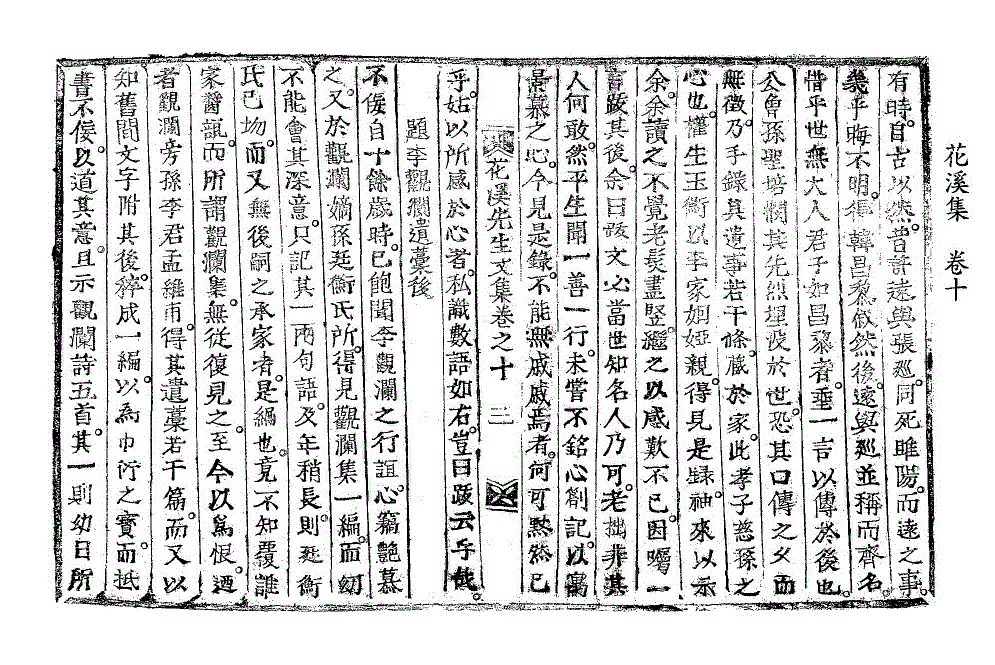 有时。自古以然。昔许远与张巡。同死雎阳。而远之事。几乎晦不明。得韩昌黎叙然后。远与巡并称而齐名。惜乎世无大人君子如昌黎者。垂一言以传于后也。公曾孙圣培悯其先烈埋没于世。恐其口传之久而无徵。乃手录其遗事若干条。藏于家。此孝子慈孙之心也。权生玉衡以李家姻娅亲。得见是录。袖来以示余。余读之不觉老发尽竖。继之以感叹不已。因嘱一言跋其后。余曰跋文必当世知名人乃可。老拙非其人何敢。然平生闻一善一行。未尝不铭心劄记。以寓景慕之心。今见是录。不能无戚戚焉者。何可默然已乎。姑以所感于心者。私识数语如右。岂曰跋云乎哉。
有时。自古以然。昔许远与张巡。同死雎阳。而远之事。几乎晦不明。得韩昌黎叙然后。远与巡并称而齐名。惜乎世无大人君子如昌黎者。垂一言以传于后也。公曾孙圣培悯其先烈埋没于世。恐其口传之久而无徵。乃手录其遗事若干条。藏于家。此孝子慈孙之心也。权生玉衡以李家姻娅亲。得见是录。袖来以示余。余读之不觉老发尽竖。继之以感叹不已。因嘱一言跋其后。余曰跋文必当世知名人乃可。老拙非其人何敢。然平生闻一善一行。未尝不铭心劄记。以寓景慕之心。今见是录。不能无戚戚焉者。何可默然已乎。姑以所感于心者。私识数语如右。岂曰跋云乎哉。题李观澜遗稿后
不佞自十馀岁时。已饱闻李观澜之行谊。心窃艳慕之。又于观澜嫡孙廷衡氏所。得见观澜集一编。而幼不能会其深意。只记其一两句语。及年稍长。则廷衡氏已殁。而又无后嗣之承家者。是编也。竟不知覆谁家酱瓿。而所谓观澜集。无从复见之。至今以为恨。乃者观澜旁孙李君孟维甫。得其遗藁若干篇。而又以知旧间文字附其后。稡成一编。以为巾衍之宝。而抵书不佞。以道其意。且示观澜诗五首。其一则幼日所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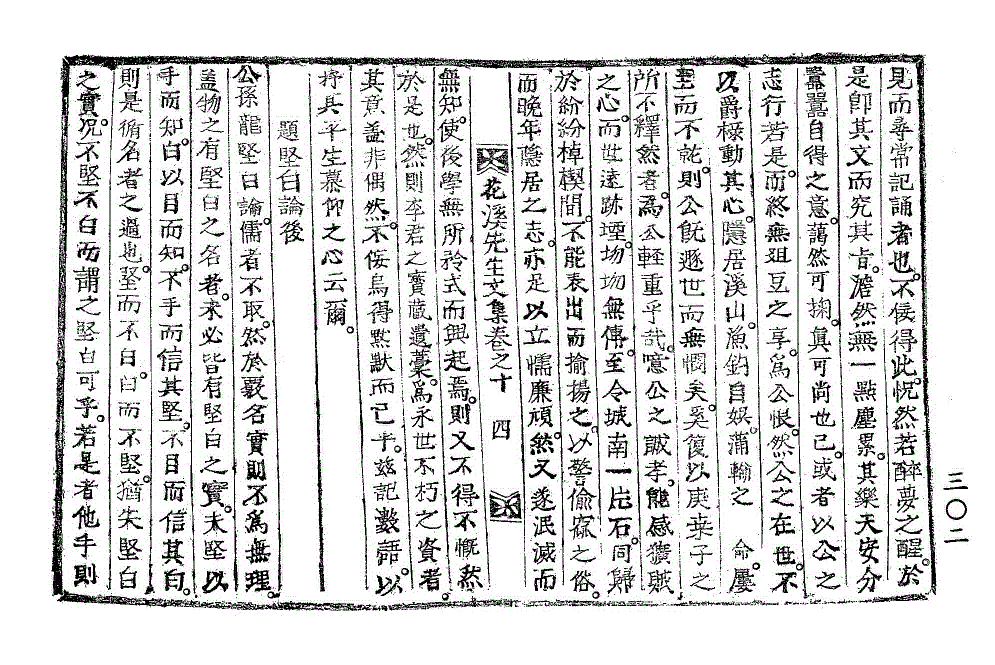 见而寻常记诵者也。不佞得此。恍然若醉梦之醒。于是即其文而究其旨。澹然无一点尘累。其乐天安分嚣嚣自得之意。蔼然可掬。真可尚也已。或者以公之志行若是。而终无俎豆之享。为公恨。然公之在世。不以爵禄动其心。隐居溪山。渔钓自娱。满轮之 命。屡至而不就。则公既遁世而无悯矣。奚复以庚桑子之所不释然者。为公轻重乎哉。噫公之诚孝。能感犷贼之心。而世远迹堙。殁殁无传。至令城南一片石。同归于纷纷棹楔间。不能表出而揄扬之。以警偷窳之俗。而晚年隐居之志。亦足以立懦廉顽。然又遂泯灭而无知。使后学无所矜式而兴起焉。则又不得不慨然于是也。然则李君之宝藏遗稿。为永世不朽之资者。其意盖非偶然。不佞乌得默默而已乎。玆记数语。以抒其平生慕仰之心云尔。
见而寻常记诵者也。不佞得此。恍然若醉梦之醒。于是即其文而究其旨。澹然无一点尘累。其乐天安分嚣嚣自得之意。蔼然可掬。真可尚也已。或者以公之志行若是。而终无俎豆之享。为公恨。然公之在世。不以爵禄动其心。隐居溪山。渔钓自娱。满轮之 命。屡至而不就。则公既遁世而无悯矣。奚复以庚桑子之所不释然者。为公轻重乎哉。噫公之诚孝。能感犷贼之心。而世远迹堙。殁殁无传。至令城南一片石。同归于纷纷棹楔间。不能表出而揄扬之。以警偷窳之俗。而晚年隐居之志。亦足以立懦廉顽。然又遂泯灭而无知。使后学无所矜式而兴起焉。则又不得不慨然于是也。然则李君之宝藏遗稿。为永世不朽之资者。其意盖非偶然。不佞乌得默默而已乎。玆记数语。以抒其平生慕仰之心云尔。题坚白论后
公孙龙坚白论。儒者不取。然于覈名实则不为无理。盖物之有坚白之名者。未必皆有坚白之实。夫坚以手而知。白以目而知。不手而信其坚。不目而信其白。则是循名者之过也。坚而不白。白而不坚。犹失坚白之实。况不坚不白而谓之坚白可乎。若是者他手则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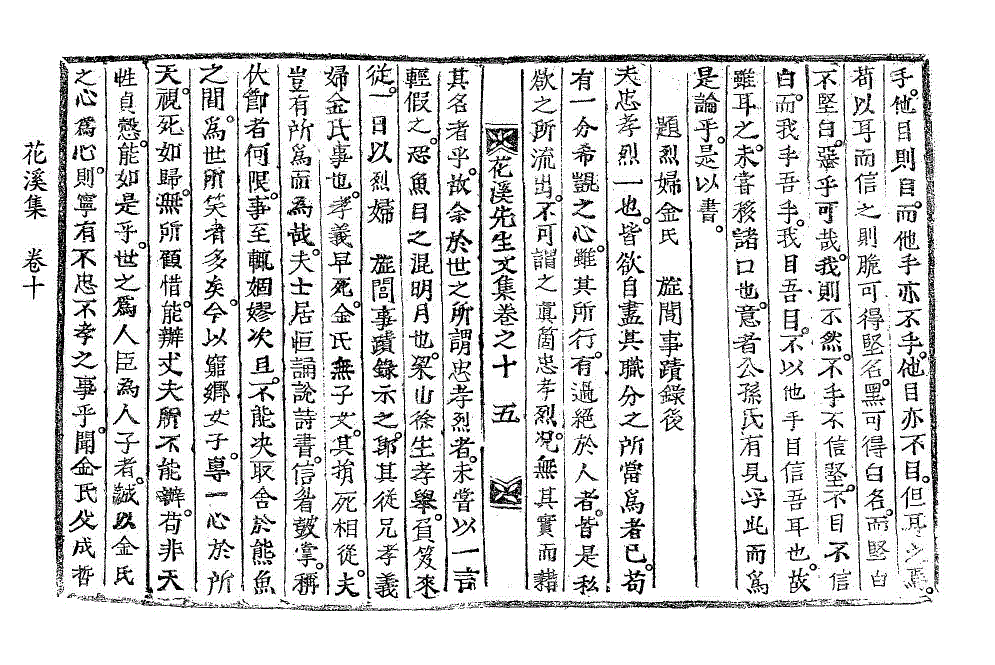 手。他目则目。而他手亦不手。他目亦不目。但耳之焉。苟以耳而信之则脆可得坚名。黑可得白名。而坚白不坚白。恶乎可哉。我则不然。不手不信坚。不目不信白。而我手吾手。我目吾目。不以他手目信吾耳也。故虽耳之。未尝移诸口也。意者公孙氏有见乎此而为是论乎。是以书。
手。他目则目。而他手亦不手。他目亦不目。但耳之焉。苟以耳而信之则脆可得坚名。黑可得白名。而坚白不坚白。恶乎可哉。我则不然。不手不信坚。不目不信白。而我手吾手。我目吾目。不以他手目信吾耳也。故虽耳之。未尝移诸口也。意者公孙氏有见乎此而为是论乎。是以书。题烈妇金氏 㫌闾事迹录后
夫忠孝烈一也。皆欲自尽其职分之所当为者已。苟有一分希觊之心。虽其所行。有过绝于人者。皆是私欲之所流出。不可谓之真个忠孝烈。况无其实而藉其名者乎。故余于世之所谓忠孝烈者。未尝以一言轻假之。恐鱼目之混明月也。梁山徐生孝举。负笈来从。一日以烈妇 㫌闾事迹录示之。即其从兄孝义妇金氏事也。孝义早死。金氏无子女。其捐死相从。夫岂有所为而为哉。夫士居恒诵说诗书。信眉鼓掌。称伏节者何限。事至辄婟嫪次且。不能决取舍于熊鱼之间。为世所笑者多矣。今以穷乡女子。专一心于所天。视死如归。无所顾惜。能办丈夫所不能办。苟非天性贞悫。能如是乎。世之为人臣为人子者。诚以金氏之心为心。则宁有不忠不孝之事乎。闻金氏父成哲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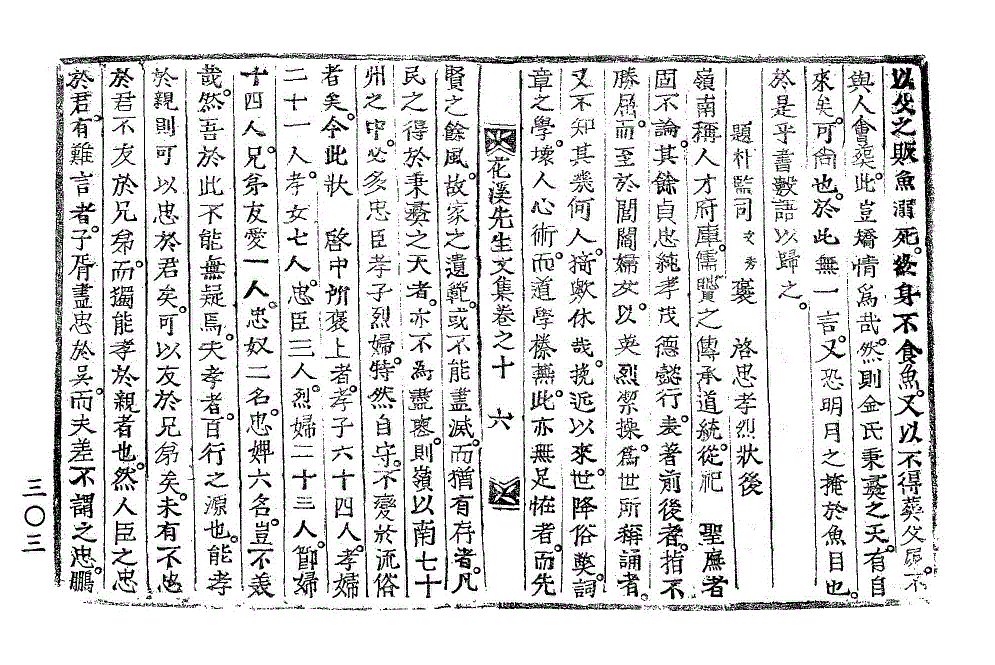 以父之贩鱼溺死。终身不食鱼。又以不得葬父尸。不与人会葬。此岂矫情为哉。然则金氏秉彝之天。有自来矣。可尚也。于此无一言。又恐明月之掩于鱼目也。于是乎书数语以归之。
以父之贩鱼溺死。终身不食鱼。又以不得葬父尸。不与人会葬。此岂矫情为哉。然则金氏秉彝之天。有自来矣。可尚也。于此无一言。又恐明月之掩于鱼目也。于是乎书数语以归之。题朴监司(文秀)褒 启忠孝烈状后
岭南称人才府库。儒贤之传承道统。从祀 圣庑者固不论。其馀贞忠纯孝茂德懿行。表著前后者。指不胜屈。而至于闾阎妇女。以英烈洁操。为世所称诵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猗欤休哉。挽近以来。世降俗弊。词章之学。坏人心术。而道学榛芜。此亦无足怪者。而先贤之馀风。故家之遗范。或不能尽灭。而犹有存者。凡民之得于秉彝之天者。亦不为尽丧。则岭以南七十州之中。必多忠臣孝子烈妇。特然自守。不变于流俗者矣。今此状 启中所褒上者。孝子六十四人。孝妇二十一人。孝女七人。忠臣三人。烈妇二十三人。节妇十四人。兄弟友爱一人。忠奴二名。忠婢六名。岂不美哉。然吾于此不能无疑焉。夫孝者。百行之源也。能孝于亲则可以忠于君矣。可以友于兄弟矣。未有不忠于君不友于兄弟。而独能孝于亲者也。然人臣之忠于君。有难言者。子胥尽忠于吴。而夫差不谓之忠。鹏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4H 页
 举竭力于宋。而高宗不谓之忠。卢杞奸邪而德宗以为忠。黄皓谄媚而后帝以为忠。古今如此者多矣。若夫孝友则一行也。孝于亲者。必能友于兄弟。友于兄弟者。必能孝于亲。此非两截事也。今所称孝子孝妇孝女合九十二人。而友兄弟者止一人何也。岂兄弟友爱。果有难于孝其亲耶。呜呼。卧冰跃鲤。王祥以孝闻。而冰鲤多跃于世矣。泣冬生笋。孟宗以孝称。而冬笋多生于后矣。割股和药。鄠人以孝㫌其门。而天下之割股㫌门者纷然矣。而孝子自此多矣。吾尝闻某人孝。问其所以为孝。则曰某也亲病断指。某也有如许感应之事。夫断指与割股相类。而割股事。朱子及退陶老先生已有定论。不必多谈。而至于感应之事。则尤茫昧慌惑而不可知也。古今称孝。以大舜曾子为至。而未闻其时有某事感应。而其所称者则惟夔夔齐慄也。启手启足也。不幸王鲤孟笋。出于经常之外。而遂为天下后世之藉口。以废其日用常行之道。而必求其奇侅异迹。以證其诚孝之感。亦足以观世变矣。然此可以诳愚蠢村氓。而又恐其不足取信于稍有知识者。则又窃取古人生事死葬之行迹。肆然笔之于书。以涂人目而簧人口。以诱邻里。邻里欺官
举竭力于宋。而高宗不谓之忠。卢杞奸邪而德宗以为忠。黄皓谄媚而后帝以为忠。古今如此者多矣。若夫孝友则一行也。孝于亲者。必能友于兄弟。友于兄弟者。必能孝于亲。此非两截事也。今所称孝子孝妇孝女合九十二人。而友兄弟者止一人何也。岂兄弟友爱。果有难于孝其亲耶。呜呼。卧冰跃鲤。王祥以孝闻。而冰鲤多跃于世矣。泣冬生笋。孟宗以孝称。而冬笋多生于后矣。割股和药。鄠人以孝㫌其门。而天下之割股㫌门者纷然矣。而孝子自此多矣。吾尝闻某人孝。问其所以为孝。则曰某也亲病断指。某也有如许感应之事。夫断指与割股相类。而割股事。朱子及退陶老先生已有定论。不必多谈。而至于感应之事。则尤茫昧慌惑而不可知也。古今称孝。以大舜曾子为至。而未闻其时有某事感应。而其所称者则惟夔夔齐慄也。启手启足也。不幸王鲤孟笋。出于经常之外。而遂为天下后世之藉口。以废其日用常行之道。而必求其奇侅异迹。以證其诚孝之感。亦足以观世变矣。然此可以诳愚蠢村氓。而又恐其不足取信于稍有知识者。则又窃取古人生事死葬之行迹。肆然笔之于书。以涂人目而簧人口。以诱邻里。邻里欺官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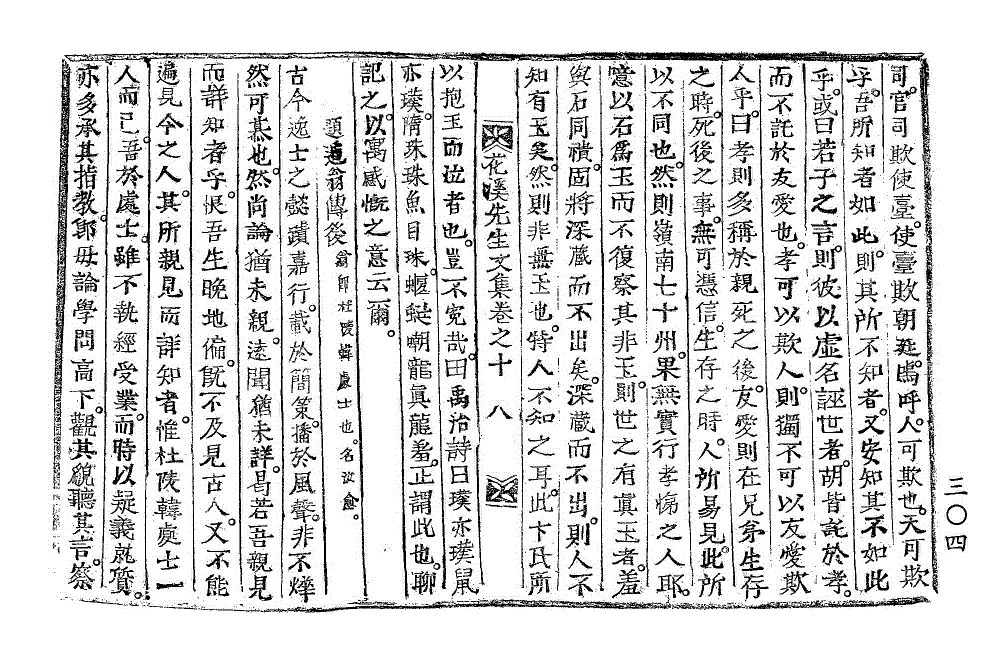 司。官司欺使台。使台欺朝廷。呜呼。人可欺也。天可欺乎。吾所知者如此。则其所不知者。又安知其不如此乎。或曰若子之言。则彼以虚名诬世者。胡皆托于孝。而不托于友爱也。孝可以欺人。则独不可以友爱欺人乎。曰孝则多称于亲死之后。友爱则在兄弟生存之时。死后之事。无可凭信。生存之时。人所易见。此所以不同也。然则岭南七十州。果无实行孝悌之人耶。噫。以石为玉而不复察其非玉。则世之有真玉者。羞与石同䙌。固将深藏而不出矣。深藏而不出。则人不知有玉矣。然则非无玉也。特人不知之耳。此卞氏所以抱玉而泣者也。岂不冤哉。田禹治诗曰璞亦璞鼠亦璞。隋珠珠鱼目珠。蝘蜓嘲龙真龙羞。正谓此也。聊记之。以寓感慨之意云尔。
司。官司欺使台。使台欺朝廷。呜呼。人可欺也。天可欺乎。吾所知者如此。则其所不知者。又安知其不如此乎。或曰若子之言。则彼以虚名诬世者。胡皆托于孝。而不托于友爱也。孝可以欺人。则独不可以友爱欺人乎。曰孝则多称于亲死之后。友爱则在兄弟生存之时。死后之事。无可凭信。生存之时。人所易见。此所以不同也。然则岭南七十州。果无实行孝悌之人耶。噫。以石为玉而不复察其非玉。则世之有真玉者。羞与石同䙌。固将深藏而不出矣。深藏而不出。则人不知有玉矣。然则非无玉也。特人不知之耳。此卞氏所以抱玉而泣者也。岂不冤哉。田禹治诗曰璞亦璞鼠亦璞。隋珠珠鱼目珠。蝘蜓嘲龙真龙羞。正谓此也。聊记之。以寓感慨之意云尔。题遁翁传后(翁即杜陵韩处士也。名汝愈。)
古今逸士之懿迹嘉行。载于简策。播于风声。非不烨然可慕也。然尚论犹未亲。远闻犹未详。曷若吾亲见而详知者乎。恨吾生晚地偏。既不及见古人。又不能遍见今之人。其所亲见而详知者。惟杜陵韩处士一人而已。吾于处士。虽不执经受业。而时以疑义就质。亦多承其指教。即毋论学问高下。观其貌听其言。察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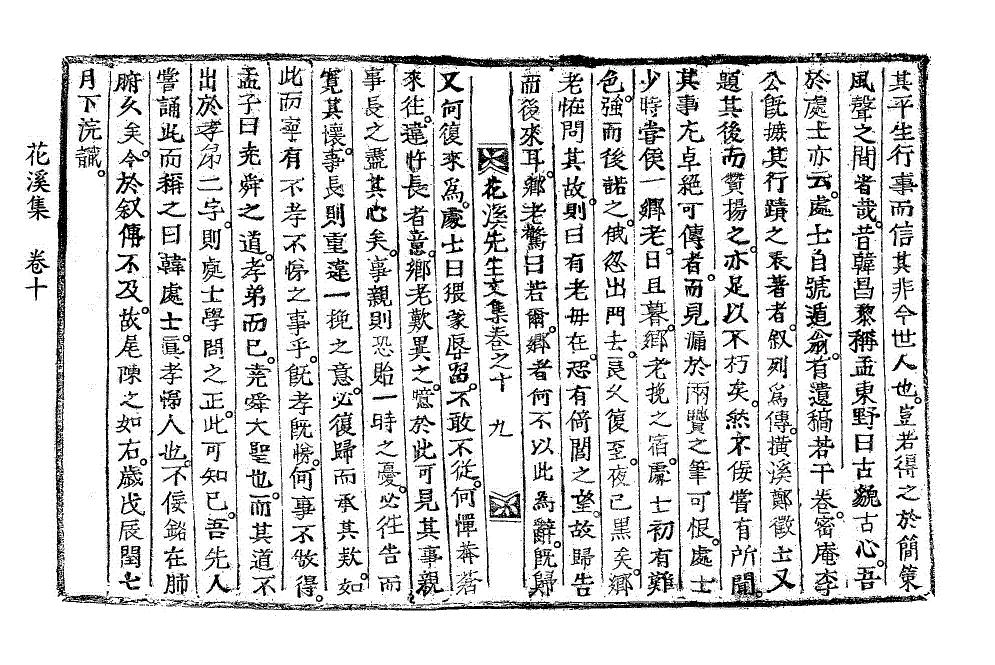 其平生行事而信其非今世人也。岂若得之于简策风声之间者哉。昔韩昌黎称孟东野曰古貌古心。吾于处士亦云。处士自号遁翁。有遗稿若干卷。密庵李公既摭其行迹之表著者。叙列为传。横溪郑徵士又题其后而赞扬之。亦足以不朽矣。然不佞尝有所闻。其事尤卓绝可传者。而见漏于两贤之笔可恨。处士少时尝候一乡老。日且暮。乡老挽之宿。处士初有难色。强而后诺之。俄忽出门去。良久复至。夜已黑矣。乡老怪问其故。则曰有老母在。恐有倚闾之望。故归告而后来耳。乡老惊曰若尔。乡者何不以此为辞。既归又何复来为。处士曰猥蒙辱留。不敢不从。何惮莽苍来往。违忤长者意。乡老叹异之。噫。于此可见其事亲事长之尽其心矣。事亲则恐贻一时之忧。必往告而宽其怀。事长则重违一挽之意。必复归而承其款。如此而宁有不孝不悌之事乎。既孝既悌。何事不做得。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尧舜大圣也。而其道不出于孝弟二字。则处士学问之正。此可知已。吾先人尝诵此而称之曰韩处士。真孝悌人也。不佞铭在肺腑久矣。今于叙传不及。故尾陈之如右。岁戊辰闰七月下浣识。
其平生行事而信其非今世人也。岂若得之于简策风声之间者哉。昔韩昌黎称孟东野曰古貌古心。吾于处士亦云。处士自号遁翁。有遗稿若干卷。密庵李公既摭其行迹之表著者。叙列为传。横溪郑徵士又题其后而赞扬之。亦足以不朽矣。然不佞尝有所闻。其事尤卓绝可传者。而见漏于两贤之笔可恨。处士少时尝候一乡老。日且暮。乡老挽之宿。处士初有难色。强而后诺之。俄忽出门去。良久复至。夜已黑矣。乡老怪问其故。则曰有老母在。恐有倚闾之望。故归告而后来耳。乡老惊曰若尔。乡者何不以此为辞。既归又何复来为。处士曰猥蒙辱留。不敢不从。何惮莽苍来往。违忤长者意。乡老叹异之。噫。于此可见其事亲事长之尽其心矣。事亲则恐贻一时之忧。必往告而宽其怀。事长则重违一挽之意。必复归而承其款。如此而宁有不孝不悌之事乎。既孝既悌。何事不做得。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尧舜大圣也。而其道不出于孝弟二字。则处士学问之正。此可知已。吾先人尝诵此而称之曰韩处士。真孝悌人也。不佞铭在肺腑久矣。今于叙传不及。故尾陈之如右。岁戊辰闰七月下浣识。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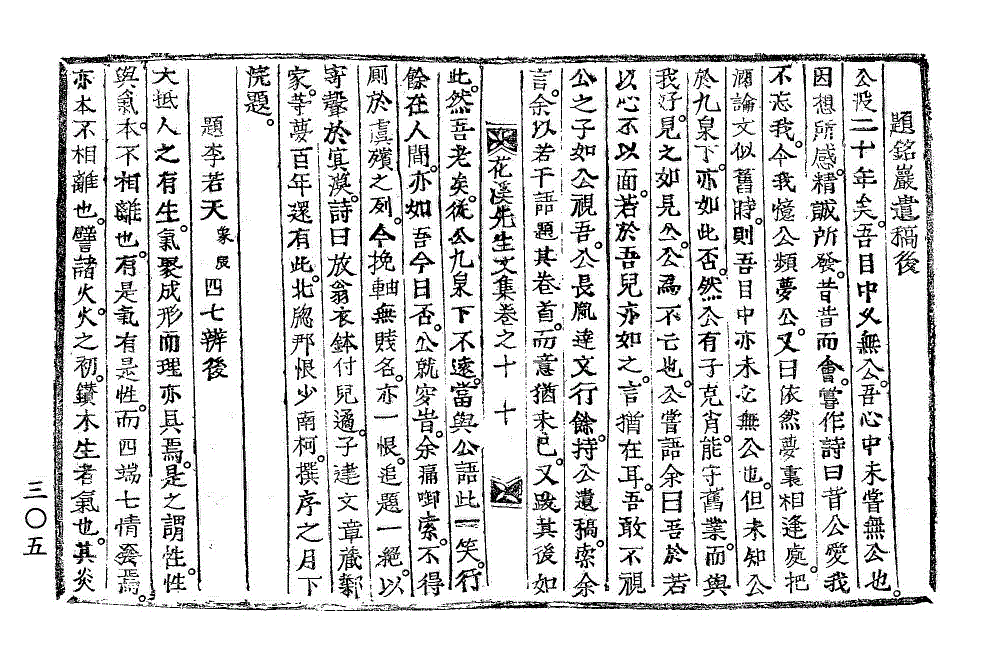 题铭岩遗稿后
题铭岩遗稿后公没二十年矣。吾目中久无公。吾心中未尝无公也。因想所感。精诚所发。昔昔而会。尝作诗曰昔公爱我不忘我。今我忆公频梦公。又曰依然梦里相逢处。把酒论文似旧时。则吾目中亦未必无公也。但未知公于九泉下。亦如此否。然公有子克肖。能守旧业。而与我好。见之如见公。公为不亡也。公尝语余曰吾于若以心不以面。若于吾儿亦如之。言犹在耳。吾敢不视公之子如公视吾。公长胤达文行馀。持公遗稿。索余言。余以若干语题其卷首。而意犹未已。又跋其后如此。然吾老矣。从公九泉下不远。当与公语此一笑。行馀在人间。亦如吾今日否。公就穸时。余痛衔索。不得厕于虞殡之列。今挽轴无贱名。亦一恨。追题一绝。以寄声于冥漠。诗曰放翁衣钵付儿遹。子建文章藏邺家。等梦百年还有此。北窗那恨少南柯。撰序之月下浣题。
题李若天(象辰)四七辨后
大抵人之有生。气聚成形而理亦具焉。是之谓性。性与气。本不相离也。有是气有是性。而四端七情发焉。亦本不相离也。譬诸火。火之初。钻木生者气也。其炎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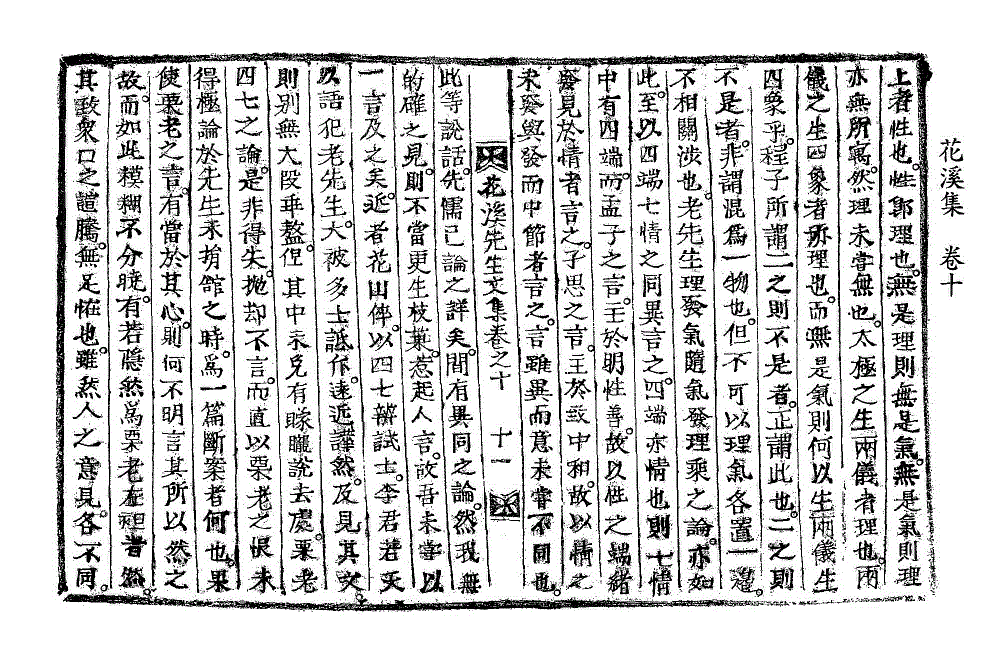 上者性也。性即理也。无是理则无是气。无是气则理亦无所寓。然理未尝无也。太极之生两仪者理也。两仪之生四象者亦理也。而无是气则何以生两仪生四象乎。程子所谓二之则不是者。正谓此也。二之则不是者。非谓混为一物也。但不可以理气各置一边。不相关涉也。老先生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论。亦如此。至以四端七情之同异言之。四端亦情也则七情中有四端。而孟子之言。主于明性善。故以性之端绪发见于情者言之。子思之言。主于致中和。故以情之未发与发而中节者言之。言虽异而意未尝不同也。此等说话。先儒已论之详矣。间有异同之论。然我无的确之见。则不当更生枝叶。惹起人言。故吾未尝以一言及之矣。近者花山倅。以四七辨试士。李君若天以语犯老先生。大被多士诋斥。远近哗然。及见其文。则别无大段乖𥂢(一作盭)。但其中未免有矇眬说去处。栗老四七之论。是非得失。抛却不言。而直以栗老之恨未得极论于先生未捐馆之时。为一篇断案者何也。果使栗老之言。有当于其心。则何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而如此模糊不分晓。有若隐然为栗老左袒者然。其致众口之諠腾。无足怪也。虽然人之意见。各不同。
上者性也。性即理也。无是理则无是气。无是气则理亦无所寓。然理未尝无也。太极之生两仪者理也。两仪之生四象者亦理也。而无是气则何以生两仪生四象乎。程子所谓二之则不是者。正谓此也。二之则不是者。非谓混为一物也。但不可以理气各置一边。不相关涉也。老先生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论。亦如此。至以四端七情之同异言之。四端亦情也则七情中有四端。而孟子之言。主于明性善。故以性之端绪发见于情者言之。子思之言。主于致中和。故以情之未发与发而中节者言之。言虽异而意未尝不同也。此等说话。先儒已论之详矣。间有异同之论。然我无的确之见。则不当更生枝叶。惹起人言。故吾未尝以一言及之矣。近者花山倅。以四七辨试士。李君若天以语犯老先生。大被多士诋斥。远近哗然。及见其文。则别无大段乖𥂢(一作盭)。但其中未免有矇眬说去处。栗老四七之论。是非得失。抛却不言。而直以栗老之恨未得极论于先生未捐馆之时。为一篇断案者何也。果使栗老之言。有当于其心。则何不明言其所以然之故。而如此模糊不分晓。有若隐然为栗老左袒者然。其致众口之諠腾。无足怪也。虽然人之意见。各不同。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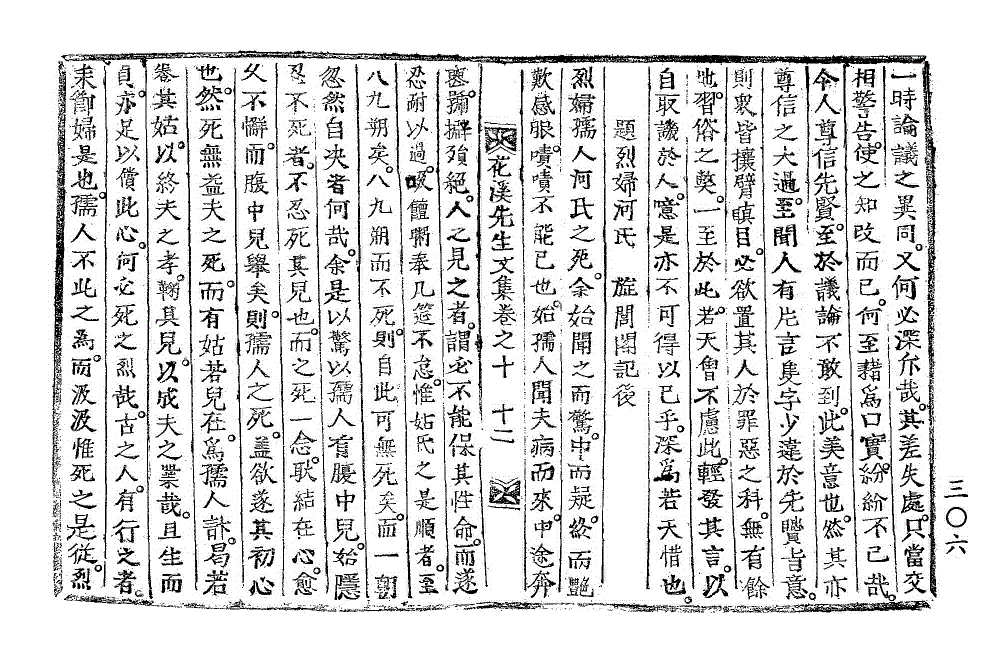 一时论议之异同。又何必深斥哉。其差失处。只当交相警告。使之知改而已。何至藉为口实。纷纷不已哉。今人尊信先贤。至于议论不敢到。此美意也。然其亦尊信之大过。至闻人有片言只字少违于先贤旨意。则众皆攘臂瞋目。必欲置其人于罪恶之科。无有馀地。习俗之弊。一至于此。若天曾不虑此。轻发其言。以自取讥于人。噫。是亦不可得以已乎。深为若天惜也。
一时论议之异同。又何必深斥哉。其差失处。只当交相警告。使之知改而已。何至藉为口实。纷纷不已哉。今人尊信先贤。至于议论不敢到。此美意也。然其亦尊信之大过。至闻人有片言只字少违于先贤旨意。则众皆攘臂瞋目。必欲置其人于罪恶之科。无有馀地。习俗之弊。一至于此。若天曾不虑此。轻发其言。以自取讥于人。噫。是亦不可得以已乎。深为若天惜也。题烈妇河氏 㫌闾阁记后
烈妇孺人河氏之死。余始闻之而惊。中而疑。终而艳叹感服。啧啧不能已也。始孺人闻夫病而来。中途奔丧。号擗殒绝。人之见之者。谓必不能保其性命。而遂忍耐以过。啜饘粥奉几筵不怠。惟姑氏之是顺者。至八九朔矣。八九朔而不死。则自此可无死矣。而一朝忽然自决者何哉。余是以惊以孺人有腹中儿。始隐忍不死者。不忍死其儿也。而之死一念。耿结在心。愈久不懈。而腹中儿举矣。则孺人之死。盖欲遂其初心也。然死无益夫之死。而有姑若儿在。为孺人计。曷若养其姑。以终夫之孝。鞠其儿。以成夫之业哉。且生而贞。亦足以偿此心。何必死之烈哉。古之人。有行之者。耒节妇是也。孺人不此之为。而汲汲惟死之是从。烈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7H 页
 则烈矣。其死得无遽乎。余是以疑也。既而徐究其所以死而得其心焉。盖有恒情之所难测者。姑不可不养。儿不可不鞠。孺人岂不念及于此。亦岂漠然忘其姑与儿哉。其心以为夫死天也。儿生亦天也。而老姑终养。有夫之二弟在。吾身有无。不足为轻重。而百年偕老之盟已矣。惟同死同穴。庶不负此心。于是付儿于天。付姑养于夫之二弟。而付其身于夫柩之侧。则生死两无憾。岂独以一死为烈哉。若耒节妇则老姑无他子。死则姑无所依。故忍死守贞。以养其姑与子固也。况孺人合卺未几。未及于归而夫死。视耒节妇友琴瑟十年者。情事又万万不同。孺人于此。盖亦计之熟矣。岂仓卒间所办哉。此余所以艳叹感服啧啧而不能已者也。噫妇事夫。犹臣事君。君有难。臣赴难同死。一时忠愤所激。忽忘其死。若时过则思之矣。思则怕死惜生之心生。遂至忍辱苟活者多矣。故急难立节易。从容就义难。昔程婴立赵孤。乃死下从。宣孟杵臼千古一人。孺人不即死。必待生腹中儿能食。乃自决以从所天于九泉下。亦妇女中程婴。非素守贞固。恶能至此。其烈行姱节。已悉于闾阁记。无复加矣。但记中有曰惟溘然速死之是快。而不暇恤焉。则何
则烈矣。其死得无遽乎。余是以疑也。既而徐究其所以死而得其心焉。盖有恒情之所难测者。姑不可不养。儿不可不鞠。孺人岂不念及于此。亦岂漠然忘其姑与儿哉。其心以为夫死天也。儿生亦天也。而老姑终养。有夫之二弟在。吾身有无。不足为轻重。而百年偕老之盟已矣。惟同死同穴。庶不负此心。于是付儿于天。付姑养于夫之二弟。而付其身于夫柩之侧。则生死两无憾。岂独以一死为烈哉。若耒节妇则老姑无他子。死则姑无所依。故忍死守贞。以养其姑与子固也。况孺人合卺未几。未及于归而夫死。视耒节妇友琴瑟十年者。情事又万万不同。孺人于此。盖亦计之熟矣。岂仓卒间所办哉。此余所以艳叹感服啧啧而不能已者也。噫妇事夫。犹臣事君。君有难。臣赴难同死。一时忠愤所激。忽忘其死。若时过则思之矣。思则怕死惜生之心生。遂至忍辱苟活者多矣。故急难立节易。从容就义难。昔程婴立赵孤。乃死下从。宣孟杵臼千古一人。孺人不即死。必待生腹中儿能食。乃自决以从所天于九泉下。亦妇女中程婴。非素守贞固。恶能至此。其烈行姱节。已悉于闾阁记。无复加矣。但记中有曰惟溘然速死之是快。而不暇恤焉。则何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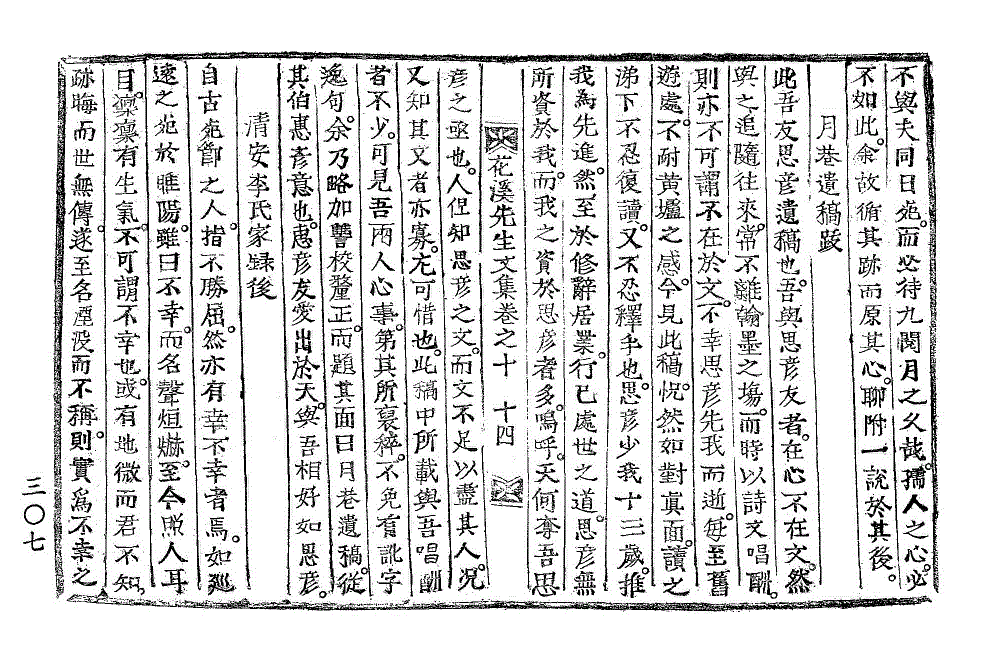 不与夫同日死。而必待九阅月之久哉。孺人之心。必不如此。余故循其迹而原其心。聊附一说于其后。
不与夫同日死。而必待九阅月之久哉。孺人之心。必不如此。余故循其迹而原其心。聊附一说于其后。月巷遗稿跋
此吾友思彦遗稿也。吾与思彦友者。在心不在文。然与之追随往来。常不离翰墨之场。而时以诗文唱酬。则亦不可谓不在于文。不幸思彦先我而逝。每至旧游处。不耐黄垆之感。今见此稿。恍然如对真面。读之涕下不忍复读。又不忍释手也。思彦少我十三岁。推我为先进。然至于修辞居业。行己处世之道。思彦无所资于我。而我之资于思彦者多。呜呼。天何夺吾思彦之亟也。人但知思彦之文。而文不足以尽其人。况又知其文者亦寡。尤可惜也。此稿中所载与吾唱酬者不少。可见吾两人心事。第其所裒稡。不免有讹字逸句。余乃略加雠校釐正。而题其面曰月巷遗稿。从其伯惠彦意也。惠彦友爱出于天。与吾相好如思彦。
清安李氏家录后
自古死节之人。指不胜屈。然亦有幸不幸者焉。如巡,远之死于睢阳。虽曰不幸。而名声烜赫。至今照人耳目。凛凛有生气。不可谓不幸也。或有地微而君不知。迹晦而世无传。遂至名湮没而不称。则实为不幸之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8H 页
 甚。然其忠义死国之心一也。倘于野史家乘。得一二遗迹之可惩者。则可不表出揄扬。以为颓俗之劝哉。李戚若初钦仲来示其家录一通。即其五代祖伏兵将遗事也。当蛇豕荐食之日。列镇望风奔溃。人皆鼠窜之不暇。而公独承主将之命。乃与家僮数人。走死地如归。卒死于战阵之中。苟非忠义之心。弸激于内。能如是乎。其心即巡远死雎阳之心也。顾以地微而迹晦。终漏于褒赠之典。不入于太史之笔。岂不惜哉。是时公登虎榜才二年矣。未有佩符专城之任。而所领皆一时乌合之卒。虽假伏兵之号。亦无见在兵甲。徒手赴敌。其不能成功固也。当时若委以仗钺制阃。统御一方。则安知其不能迅扫卉服。使鲸海妥帖哉。虽不幸而不免于死。又安知其不如巡远之保障江淮。以济中兴之功哉。今乃生而不幸。不见知于明主。死又不幸。埋没于虫沙之间。而使忠义之心。终不白于后世。则千秋志士之恨。当何如也。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则平日事亲之孝。即此可知。而公之先祖有死节于丽朝者。则亦可见其有自来矣。恨余学识浅短。不能作传以褒张之。秪自钦艳咄叹而已。世之君子。倘能叙其事而曝其心。以传于世。不至于泯灭。则
甚。然其忠义死国之心一也。倘于野史家乘。得一二遗迹之可惩者。则可不表出揄扬。以为颓俗之劝哉。李戚若初钦仲来示其家录一通。即其五代祖伏兵将遗事也。当蛇豕荐食之日。列镇望风奔溃。人皆鼠窜之不暇。而公独承主将之命。乃与家僮数人。走死地如归。卒死于战阵之中。苟非忠义之心。弸激于内。能如是乎。其心即巡远死雎阳之心也。顾以地微而迹晦。终漏于褒赠之典。不入于太史之笔。岂不惜哉。是时公登虎榜才二年矣。未有佩符专城之任。而所领皆一时乌合之卒。虽假伏兵之号。亦无见在兵甲。徒手赴敌。其不能成功固也。当时若委以仗钺制阃。统御一方。则安知其不能迅扫卉服。使鲸海妥帖哉。虽不幸而不免于死。又安知其不如巡远之保障江淮。以济中兴之功哉。今乃生而不幸。不见知于明主。死又不幸。埋没于虫沙之间。而使忠义之心。终不白于后世。则千秋志士之恨。当何如也。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则平日事亲之孝。即此可知。而公之先祖有死节于丽朝者。则亦可见其有自来矣。恨余学识浅短。不能作传以褒张之。秪自钦艳咄叹而已。世之君子。倘能叙其事而曝其心。以传于世。不至于泯灭。则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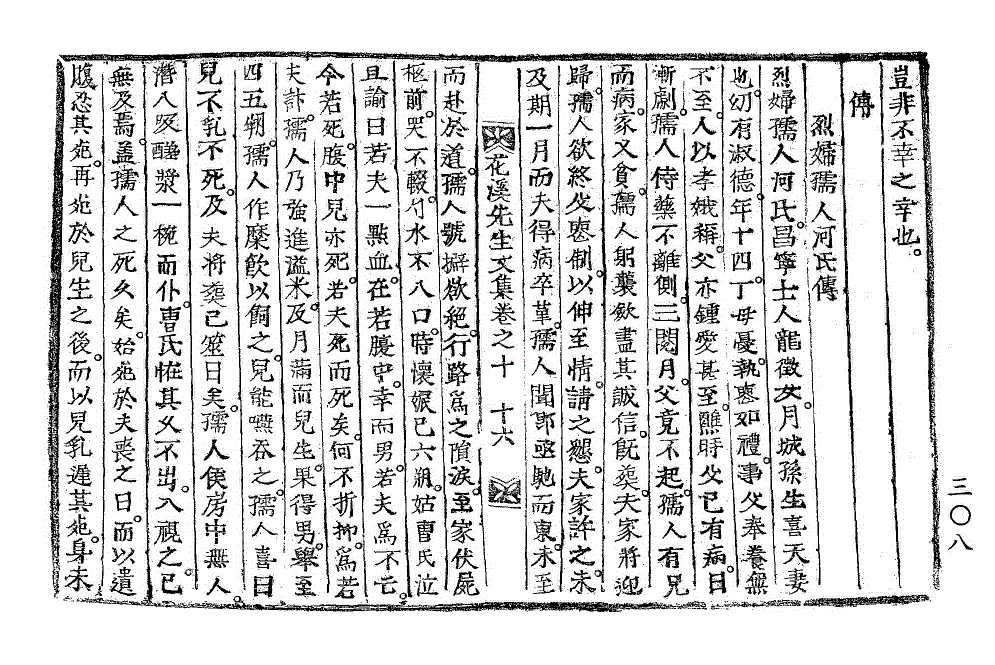 岂非不幸之幸也。
岂非不幸之幸也。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传
烈妇孺人河氏传
烈妇孺人河氏。昌宁士人龙徵女。月城孙生喜天妻也。幼有淑德。年十四。丁母忧。执丧如礼。事父奉养无不至。人以孝娥称。父亦钟爱甚至。醮时父已有病。日渐剧。孺人侍药不离侧。三阅月。父竟不起。孺人有兄而病。家又贫。孺人躬袭敛尽其诚信。既葬。夫家将迎归。孺人欲终父丧制。以伸至情。请之恳。夫家许之。未及期一月而夫得病卒革。孺人闻即亟驰而东。未至而赴于道。孺人号擗欲绝。行路为之陨泪。至家伏尸柩前。哭不辍。勺水不入口。时怀娠已六朔。姑曹氏泣且谕曰若夫一点血。在若腹中。幸而男。若夫为不亡。今若死。腹中儿亦死。若夫死而死矣。何不折抑。为若夫计。孺人乃强进溢米。及月满而儿生。果得男。举至四五朔。孺人作糜饮以饲之。儿能咽吞之。孺人喜曰儿不乳不死。及夫将葬已筮日矣。孺人候房中无人。潜入吸醝浆一碗而仆。曹氏怪其久不出。入视之。已无及焉。盖孺人之死久矣。始死于夫丧之日。而以遗腹忍其死。再死于儿生之后。而以儿乳迟其死。身未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9H 页
 死而心则死已久矣。至是身与心俱死。则人始信其死之烈。时距夫葬期隔五日。死于其前者。亦欲遂其同穴之愿。其家遂改卜日而同窆焉。初孺人卧儿笼架下。一日儿急啼。孺人怪之。即移卧他处。俄而架折笼压而儿得免。异哉。岂天以孺人至諴。默诱而全之耶。儿名友觉。今长而室有子矣。为人亦纯悫。守天性。不愧为孺人子。昌宁之河。系出晋山府院君崙。故孺人贯晋阳。孙亦庆之望族。即判书景节公后。而孙生亦佳士。两家家世相敌。夫妇亦相得。而不克享其福寿。惜哉。州上其事方伯。方伯闻于 朝。特 命㫌其闾。闾在鸡林府皇南里。
死而心则死已久矣。至是身与心俱死。则人始信其死之烈。时距夫葬期隔五日。死于其前者。亦欲遂其同穴之愿。其家遂改卜日而同窆焉。初孺人卧儿笼架下。一日儿急啼。孺人怪之。即移卧他处。俄而架折笼压而儿得免。异哉。岂天以孺人至諴。默诱而全之耶。儿名友觉。今长而室有子矣。为人亦纯悫。守天性。不愧为孺人子。昌宁之河。系出晋山府院君崙。故孺人贯晋阳。孙亦庆之望族。即判书景节公后。而孙生亦佳士。两家家世相敌。夫妇亦相得。而不克享其福寿。惜哉。州上其事方伯。方伯闻于 朝。特 命㫌其闾。闾在鸡林府皇南里。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论
反六逆论
昔卫石碏有六逆之说。谓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柳子厚作论以非之。以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甚矣子厚之偏滞也。其言曰晋疠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独不见废宜臼立伯服。而周召犬戎之祸乎。又曰秦用张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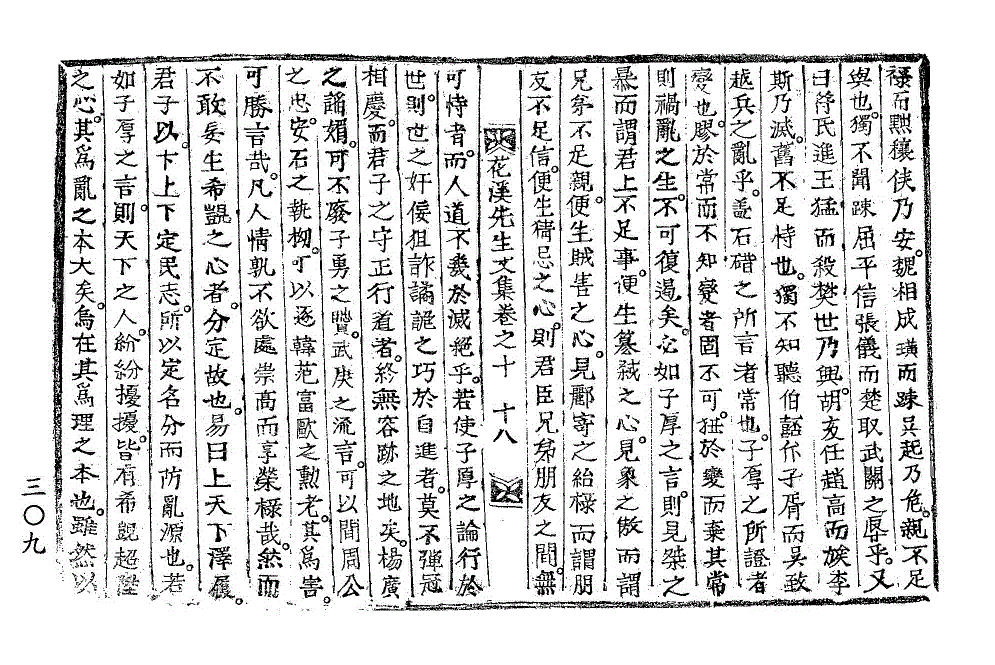 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独不闻疏屈平信张仪而楚取武关之辱乎。又曰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独不知听伯嚭斥子胥而吴致越兵之乱乎。盖石碏之所言者常也。子厚之所證者变也。胶于常而不知变者固不可。狃于变而弃其常则祸乱之生。不可复遏矣。必如子厚之言。则见桀之暴而谓君上不足事。便生篡弑之心。见象之傲而谓兄弟不足亲。便生贼害之心。见郦寄之绐禄而谓朋友不足信。便生猜忌之心。则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可恃者。而人道不几于灭绝乎。若使子厚之论行于世。则世之奸佞狙诈谲诡之巧于自进者。莫不弹冠相庆。而君子之守正行道者。终无容迹之地矣。杨广之谄媚。可不(一作以)废子勇之贤。武庚之流言。可以间周公之忠。安石之执拗。可以逐韩范富欧之勋老。其为害。可胜言哉。凡人情孰不欲处崇高而享荣禄哉。然而不敢妄生希觊之心者。分定故也。易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卞上下定民志。所以定名分而防乱源也。若如子厚之言。则天下之人。纷纷扰扰。皆有希觊超升之心。其为乱之本大矣。乌在其为理之本也。虽然以
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独不闻疏屈平信张仪而楚取武关之辱乎。又曰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独不知听伯嚭斥子胥而吴致越兵之乱乎。盖石碏之所言者常也。子厚之所證者变也。胶于常而不知变者固不可。狃于变而弃其常则祸乱之生。不可复遏矣。必如子厚之言。则见桀之暴而谓君上不足事。便生篡弑之心。见象之傲而谓兄弟不足亲。便生贼害之心。见郦寄之绐禄而谓朋友不足信。便生猜忌之心。则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可恃者。而人道不几于灭绝乎。若使子厚之论行于世。则世之奸佞狙诈谲诡之巧于自进者。莫不弹冠相庆。而君子之守正行道者。终无容迹之地矣。杨广之谄媚。可不(一作以)废子勇之贤。武庚之流言。可以间周公之忠。安石之执拗。可以逐韩范富欧之勋老。其为害。可胜言哉。凡人情孰不欲处崇高而享荣禄哉。然而不敢妄生希觊之心者。分定故也。易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卞上下定民志。所以定名分而防乱源也。若如子厚之言。则天下之人。纷纷扰扰。皆有希觊超升之心。其为乱之本大矣。乌在其为理之本也。虽然以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0H 页
 子厚之识见。宁不觑得乎此。而其为此论者。抑亦有由然矣。当其附王伾,叔文之时。行事诡秘而所为多间亲间旧之事。与伾文等内外唱和。欲专其权柄。则又安知其无以贱妨贵之心乎。及德宗即位。伾文败死而八司马皆被斥黜。则其情状可见也。子厚之为此论。无乃欲护伾文专擅之罪。而隐然掩其党附之迹。若尔则其言出于矫情饰辞。而非其本心也欤。
子厚之识见。宁不觑得乎此。而其为此论者。抑亦有由然矣。当其附王伾,叔文之时。行事诡秘而所为多间亲间旧之事。与伾文等内外唱和。欲专其权柄。则又安知其无以贱妨贵之心乎。及德宗即位。伾文败死而八司马皆被斥黜。则其情状可见也。子厚之为此论。无乃欲护伾文专擅之罪。而隐然掩其党附之迹。若尔则其言出于矫情饰辞。而非其本心也欤。五王不诛武氏论
胡致堂以五王不诛武氏。为不能以大义处非常之变。为唐室讨罪人。愚尝读史至此。不能无疑焉。夫武氏之罪。固如致堂之论。虽诛其身而灭其族。夫孰曰不可。而但其间有难处者。既立中宗。则中宗是谁之子也。立其子而诛其母。其于天理人情。何如也。就以致堂所證文姜哀姜之事言之。春秋书夫人逊于斋。逊者顺让之嗣。使若不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未尝以鲁人之不诛姜氏为罪。则五王亦乌得立其君而遽诛其君之母乎。父母天地也。不可有天而无地。则人岂可有父而无母乎。致堂谓中宗无所与焉者。亦有所不然。昔赵穿手刃灵公。而赵盾蒙弑君之名。以盾为正卿也。况中宗虽幽废东宫。而拨乱反正。人皆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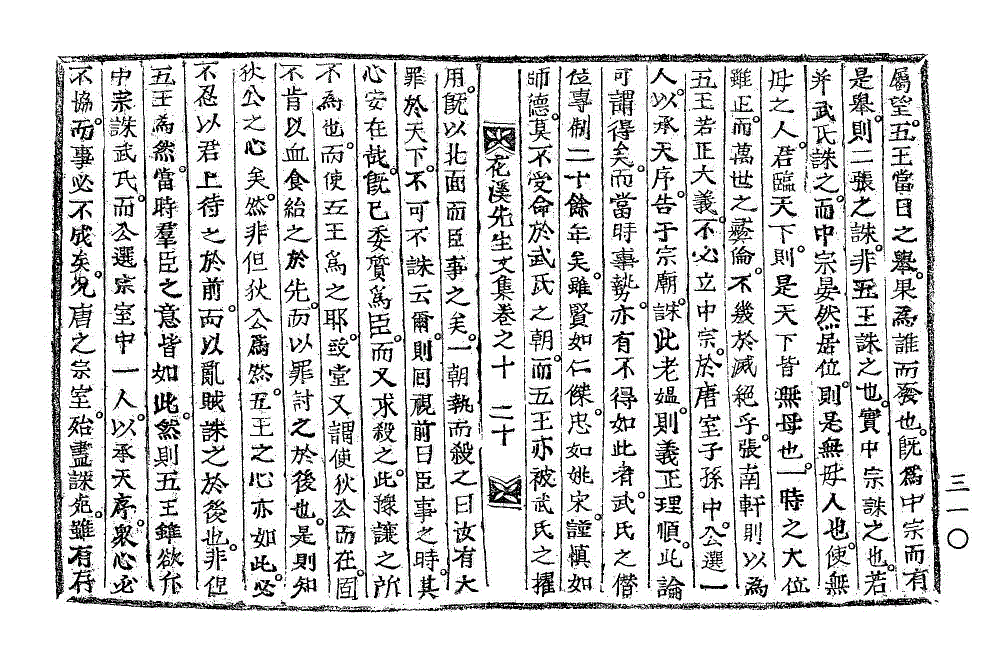 属望。五王当日之举。果为谁而发也。既为中宗而有是举。则二张之诛。非五王诛之也。实中宗诛之也。若并武氏诛之。而中宗晏然居位。则是无母人也。使无母之人。君临天下。则是天下皆无母也。一时之大位虽正。而万世之彝伦。不几于灭绝乎。张南轩则以为五王若正大义。不必立中宗。于唐室子孙中。公选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庙。诛此老媪。则义正理顺。此论可谓得矣。而当时事势。亦有不得如此者。武氏之僭位专制二十馀年矣。虽贤如仁杰。忠如姚宋。谨慎如师德。莫不受命于武氏之朝。而五王亦被武氏之擢用。既以北面而臣事之矣。一朝执而杀之曰汝有大罪于天下。不可不诛云尔。则回视前日臣事之时。其心安在哉。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此豫让之所不为也。而使五王为之耶。致堂又谓使狄公而在。固不肯以血食绐之于先。而以罪讨之于后也。是则知狄公之心矣。然非但狄公为然。五王之心亦如此。必不忍以君上待之于前。而以乱贼诛之于后也。非但五王为然。当时群臣之意皆如此。然则五王虽欲斥中宗诛武氏而公选宗室中一人。以承天序。众心必不协。而事必不成矣。况唐之宗室。殆尽诛死。虽有存
属望。五王当日之举。果为谁而发也。既为中宗而有是举。则二张之诛。非五王诛之也。实中宗诛之也。若并武氏诛之。而中宗晏然居位。则是无母人也。使无母之人。君临天下。则是天下皆无母也。一时之大位虽正。而万世之彝伦。不几于灭绝乎。张南轩则以为五王若正大义。不必立中宗。于唐室子孙中。公选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庙。诛此老媪。则义正理顺。此论可谓得矣。而当时事势。亦有不得如此者。武氏之僭位专制二十馀年矣。虽贤如仁杰。忠如姚宋。谨慎如师德。莫不受命于武氏之朝。而五王亦被武氏之擢用。既以北面而臣事之矣。一朝执而杀之曰汝有大罪于天下。不可不诛云尔。则回视前日臣事之时。其心安在哉。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此豫让之所不为也。而使五王为之耶。致堂又谓使狄公而在。固不肯以血食绐之于先。而以罪讨之于后也。是则知狄公之心矣。然非但狄公为然。五王之心亦如此。必不忍以君上待之于前。而以乱贼诛之于后也。非但五王为然。当时群臣之意皆如此。然则五王虽欲斥中宗诛武氏而公选宗室中一人。以承天序。众心必不协。而事必不成矣。况唐之宗室。殆尽诛死。虽有存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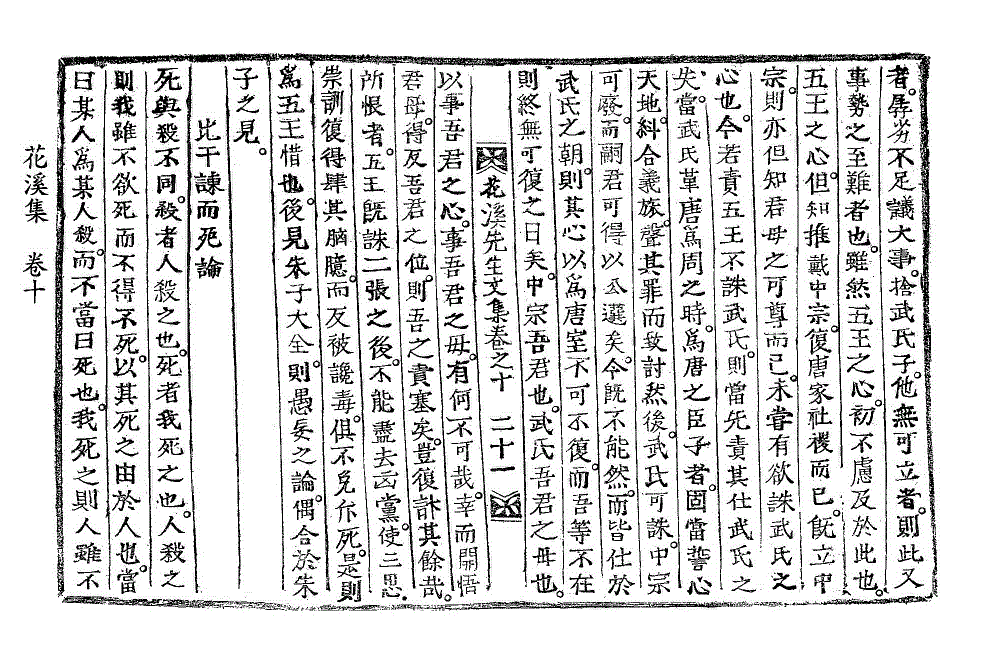 者。孱劣不足议大事。舍武氏子。他无可立者。则此又事势之至难者也。虽然五王之心。初不虑及于此也。五王之心。但知推戴中宗。复唐家社稷而已。既立中宗。则亦但知君母之可尊而已。未尝有欲诛武氏之心也。今若责五王不诛武氏。则当先责其仕武氏之失。当武氏革唐为周之时。为唐之臣子者。固当誓心天地。纠合义旅。声其罪而致讨然后。武氏可诛。中宗可废。而嗣君可得以公选矣。今既不能然。而皆仕于武氏之朝。则其心以为唐室不可不复。而吾等不在则终无可复之日矣。中宗吾君也。武氏吾君之母也。以事吾君之心。事吾君之母。有何不可哉。幸而开悟君母。得反吾君之位。则吾之责塞矣。岂复计其馀哉。所恨者。五王既诛二张之后。不能尽去凶党。使三思,崇训复得肆其胸臆。而反被谗毒。俱不免斥死。是则为五王惜也。后见朱子大全。则愚妄之论。偶合于朱子之见。
者。孱劣不足议大事。舍武氏子。他无可立者。则此又事势之至难者也。虽然五王之心。初不虑及于此也。五王之心。但知推戴中宗。复唐家社稷而已。既立中宗。则亦但知君母之可尊而已。未尝有欲诛武氏之心也。今若责五王不诛武氏。则当先责其仕武氏之失。当武氏革唐为周之时。为唐之臣子者。固当誓心天地。纠合义旅。声其罪而致讨然后。武氏可诛。中宗可废。而嗣君可得以公选矣。今既不能然。而皆仕于武氏之朝。则其心以为唐室不可不复。而吾等不在则终无可复之日矣。中宗吾君也。武氏吾君之母也。以事吾君之心。事吾君之母。有何不可哉。幸而开悟君母。得反吾君之位。则吾之责塞矣。岂复计其馀哉。所恨者。五王既诛二张之后。不能尽去凶党。使三思,崇训复得肆其胸臆。而反被谗毒。俱不免斥死。是则为五王惜也。后见朱子大全。则愚妄之论。偶合于朱子之见。比干谏而死论
死与杀不同。杀者人杀之也。死者我死之也。人杀之则我虽不欲死而不得不死。以其死之由于人也。当曰某人为某人杀。而不当曰死也。我死之则人虽不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1L 页
 欲杀。而亦不得不杀。以其杀之由于我也。当曰某人以某事死。而不当曰杀也。然则其杀虽同。而其所以杀则不同。其死虽同。而其所以死则不同。其杀也以道。其死也不以义。则可谓之杀。而不可谓之死也。其死也以义。而其杀也不以道。则可谓之死。而不可谓之杀也。死与杀之间。相去不能以寸。而是非得失之分。不啻天壤矣。此不可不察也。昔比干谏于纣。纣怒而杀之。则是比干被杀于纣。而孔子称殷之三仁。乃曰比干谏而死。有若自死者然。盖推其心之所在而许其死也。当纣之淫虐不悛也。商之忠臣义士。不为不多。如胶鬲,祖伊之辈。何尝不尽忠王室。亦何尝不谏纣之非。而纣未尝杀焉。则比干之见杀。非纣杀之也。乃比干自死也。其言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观于此言。可见其志之所在也。当是时。纣之虐杀无辜何如也。朝涉之胫则斮杀之矣。孕妇之腹则刳杀之矣。而缘铜柱坠烈火。见杀于纣者。不可胜记。则批逆鳞触怒牙。可知其必不免其吞噬。而乃敢直言极谏。三日而不去。则其志在于必死而后已。纣安得不杀哉。杀之者纣。而死之者比干也。不然箕子亦尝谏矣。而纣不之杀。任其鼓琴歌而隐焉。微子亦
欲杀。而亦不得不杀。以其杀之由于我也。当曰某人以某事死。而不当曰杀也。然则其杀虽同。而其所以杀则不同。其死虽同。而其所以死则不同。其杀也以道。其死也不以义。则可谓之杀。而不可谓之死也。其死也以义。而其杀也不以道。则可谓之死。而不可谓之杀也。死与杀之间。相去不能以寸。而是非得失之分。不啻天壤矣。此不可不察也。昔比干谏于纣。纣怒而杀之。则是比干被杀于纣。而孔子称殷之三仁。乃曰比干谏而死。有若自死者然。盖推其心之所在而许其死也。当纣之淫虐不悛也。商之忠臣义士。不为不多。如胶鬲,祖伊之辈。何尝不尽忠王室。亦何尝不谏纣之非。而纣未尝杀焉。则比干之见杀。非纣杀之也。乃比干自死也。其言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观于此言。可见其志之所在也。当是时。纣之虐杀无辜何如也。朝涉之胫则斮杀之矣。孕妇之腹则刳杀之矣。而缘铜柱坠烈火。见杀于纣者。不可胜记。则批逆鳞触怒牙。可知其必不免其吞噬。而乃敢直言极谏。三日而不去。则其志在于必死而后已。纣安得不杀哉。杀之者纣。而死之者比干也。不然箕子亦尝谏矣。而纣不之杀。任其鼓琴歌而隐焉。微子亦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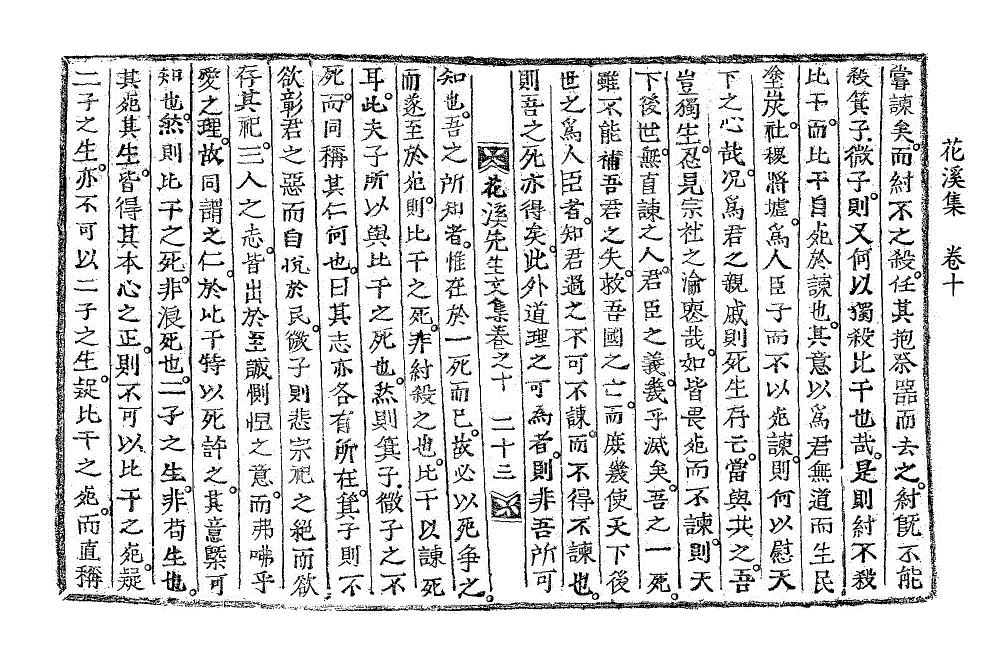 尝谏矣。而纣不之杀。任其抱祭器而去之。纣既不能杀箕子,微子。则又何以独杀比干也哉。是则纣不杀比干。而比干自死于谏也。其意以为君无道而生民涂炭。社稷将墟。为人臣子而不以死谏。则何以慰天下之心哉。况为君之亲戚则死生存亡。当与共之。吾岂独生。忍见宗社之沦丧哉。如皆畏死而不谏。则天下后世。无直谏之人。君臣之义。几乎灭矣。吾之一死。虽不能补吾君之失。救吾国之亡。而庶几使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知君过之不可不谏。而不得不谏也。则吾之死亦得矣。此外道理之可为者。则非吾所可知也。吾之所知者。惟在于一死而已。故必以死争之。而遂至于死。则比干之死。非纣杀之也。比干以谏死耳。此夫子所以与比干之死也。然则箕子,微子之不死。而同称其仁何也。曰其志亦各有所在。箕子则不欲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微子则悲宗祀之绝而欲存其祀。三人之志。皆出于至诚恻怛之意。而弗咈乎爱之理。故同谓之仁。于比干特以死许之。其意槩可知也。然则比干之死。非浪死也。二子之生。非苟生也。其死其生。皆得其本心之正。则不可以比干之死。疑二子之生。亦不可以二子之生。疑比干之死。而直称
尝谏矣。而纣不之杀。任其抱祭器而去之。纣既不能杀箕子,微子。则又何以独杀比干也哉。是则纣不杀比干。而比干自死于谏也。其意以为君无道而生民涂炭。社稷将墟。为人臣子而不以死谏。则何以慰天下之心哉。况为君之亲戚则死生存亡。当与共之。吾岂独生。忍见宗社之沦丧哉。如皆畏死而不谏。则天下后世。无直谏之人。君臣之义。几乎灭矣。吾之一死。虽不能补吾君之失。救吾国之亡。而庶几使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知君过之不可不谏。而不得不谏也。则吾之死亦得矣。此外道理之可为者。则非吾所可知也。吾之所知者。惟在于一死而已。故必以死争之。而遂至于死。则比干之死。非纣杀之也。比干以谏死耳。此夫子所以与比干之死也。然则箕子,微子之不死。而同称其仁何也。曰其志亦各有所在。箕子则不欲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微子则悲宗祀之绝而欲存其祀。三人之志。皆出于至诚恻怛之意。而弗咈乎爱之理。故同谓之仁。于比干特以死许之。其意槩可知也。然则比干之死。非浪死也。二子之生。非苟生也。其死其生。皆得其本心之正。则不可以比干之死。疑二子之生。亦不可以二子之生。疑比干之死。而直称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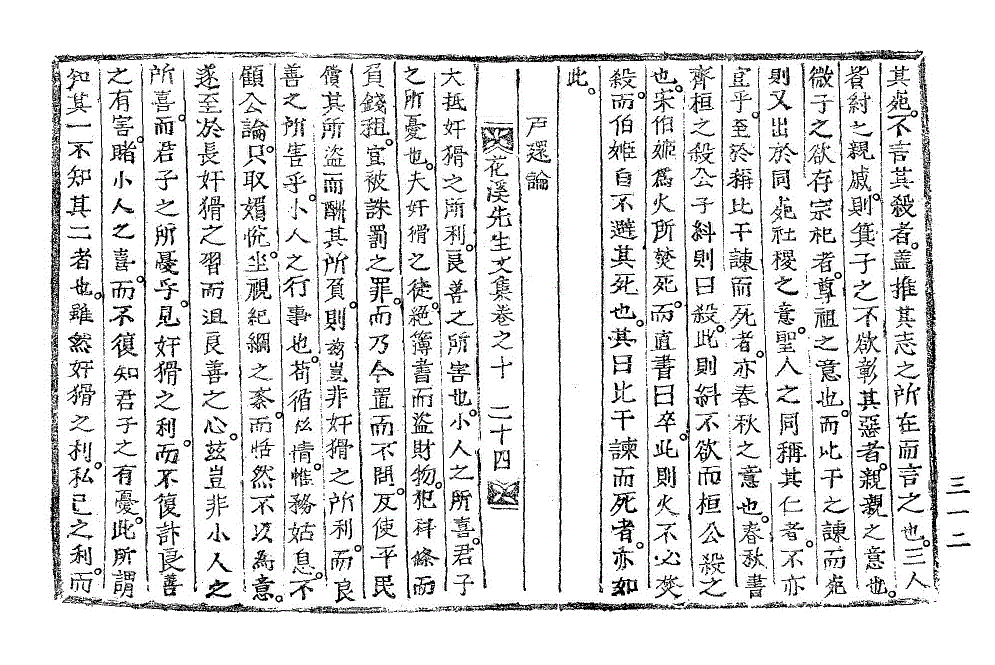 其死。不言其杀者。盖推其志之所在而言之也。三人皆纣之亲戚。则箕子之不欲彰其恶者。亲亲之意也。微子之欲存宗祀者。尊祖之意也。而比干之谏而死则又出于同死社稷之意。圣人之同称其仁者。不亦宜乎。至于称比干谏而死者。亦春秋之意也。春秋书齐桓之杀公子纠则曰杀。此则纠不欲而桓公杀之也。宋伯姬为火所焚死。而直书曰卒。此则火不必焚杀。而伯姬自不避其死也。其曰比干谏而死者。亦如此。
其死。不言其杀者。盖推其志之所在而言之也。三人皆纣之亲戚。则箕子之不欲彰其恶者。亲亲之意也。微子之欲存宗祀者。尊祖之意也。而比干之谏而死则又出于同死社稷之意。圣人之同称其仁者。不亦宜乎。至于称比干谏而死者。亦春秋之意也。春秋书齐桓之杀公子纠则曰杀。此则纠不欲而桓公杀之也。宋伯姬为火所焚死。而直书曰卒。此则火不必焚杀。而伯姬自不避其死也。其曰比干谏而死者。亦如此。户还论
大抵奸猾之所利。良善之所害也。小人之所喜。君子之所忧也。夫奸猾之徒。绝簿书而盗财物。犯科条而负钱租。宜被诛罚之罪。而乃今置而不问。反使平民偿其所盗而酬其所负。则玆岂非奸猾之所利。而良善之所害乎。小人之行事也。苟循私情。惟务姑息。不顾公论。只取媚悦。坐视纪纲之紊。而恬然不以为意。遂至于长奸猾之习而沮良善之心。玆岂非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忧乎。见奸猾之利。而不复计良善之有害。赌(一作睹)小人之喜。而不复知君子之有忧。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虽然奸猾之利。私己之利。而
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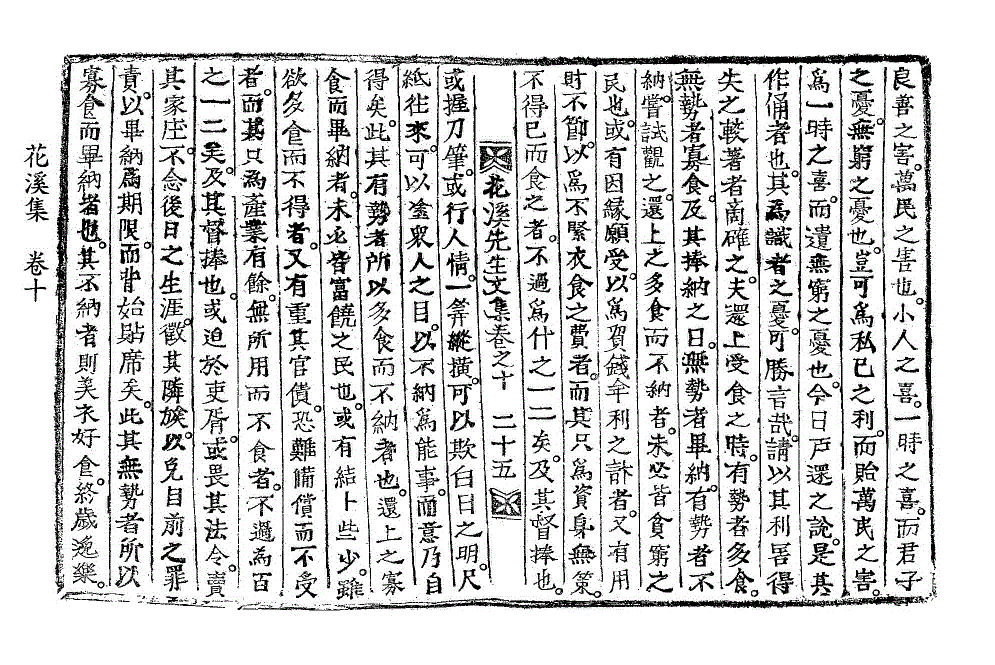 良善之害。万民之害也。小人之喜。一时之喜。而君子之忧。无穷之忧也。岂可为私己之利。而贻万民之害。为一时之喜。而遗无穷之忧也。今日户还之说。是其作俑者也。其为识者之忧。可胜言哉。请以其利害得失之较著者商确之。夫还上受食之时。有势者多食。无势者寡食。及其捧纳之日。无势者毕纳。有势者不纳。尝试观之。还上之多食而不纳者。未必皆贫穷之民也。或有因缘愿受。以为贸钱牟利之计者。又有用财不节。以为不紧衣食之费者。而其只为资身无策。不得已而食之者。不过为什之一二矣。及其督捧也。或握刀笔。或行人情。一算纵横。可以欺白日之明。尺纸往来。可以涂众人之目。以不纳为能事。而意乃自得矣。此其有势者所以多食而不纳者也。还上之寡食而毕纳者。未必皆富饶之民也。或有结卜些少。虽欲多食而不得者。又有重其官债。恐难备偿而不受者。而其只为产业有馀。无所用而不食者。不过为百之一二矣。及其督捧也。或迫于吏胥。或畏其法令。卖其家庄。不念后日之生涯。徵其邻族。以免目前之罪责。以毕纳为期限。而背始贴席矣。此其无势者所以寡食而毕纳者也。其不纳者则美衣好食。终岁逸乐。
良善之害。万民之害也。小人之喜。一时之喜。而君子之忧。无穷之忧也。岂可为私己之利。而贻万民之害。为一时之喜。而遗无穷之忧也。今日户还之说。是其作俑者也。其为识者之忧。可胜言哉。请以其利害得失之较著者商确之。夫还上受食之时。有势者多食。无势者寡食。及其捧纳之日。无势者毕纳。有势者不纳。尝试观之。还上之多食而不纳者。未必皆贫穷之民也。或有因缘愿受。以为贸钱牟利之计者。又有用财不节。以为不紧衣食之费者。而其只为资身无策。不得已而食之者。不过为什之一二矣。及其督捧也。或握刀笔。或行人情。一算纵横。可以欺白日之明。尺纸往来。可以涂众人之目。以不纳为能事。而意乃自得矣。此其有势者所以多食而不纳者也。还上之寡食而毕纳者。未必皆富饶之民也。或有结卜些少。虽欲多食而不得者。又有重其官债。恐难备偿而不受者。而其只为产业有馀。无所用而不食者。不过为百之一二矣。及其督捧也。或迫于吏胥。或畏其法令。卖其家庄。不念后日之生涯。徵其邻族。以免目前之罪责。以毕纳为期限。而背始贴席矣。此其无势者所以寡食而毕纳者也。其不纳者则美衣好食。终岁逸乐。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3L 页
 用财如流水而无所顾惜。视其积债如浮云之在天。未尝一动其心。原其情状。擢发无惜。而今乃终无捶楚之苦。以掩其罪者何也。君子赏罚之道。不宜如是之舛也。呜呼。有罪而诛之。犹惧法之不立而奸猾之莫惩也。而况置其罪而复免其人所盗之财。以优容之乎。有善而赏之。犹恐化之难行而良善之莫劝也。而况抑其善而使酬他人所负之债。以刻薄之乎。吾知此法一行。还上之多食而不纳者。愈多食而愈不纳矣。其寡食而毕纳者。亦骎骎然怠于纳矣。奸猾之徒。必将弹冠而相庆。幸其计之得售。而绝簿书盗财物。尤无所忌惮也。彼良善之民。亦将圜视而相语。以为国法不足恃。而奸谋谲计。果可以为保家保身之良策也。如此则前日之奸猾。益为奸猾。而今日之良善。又安知不亦后日之奸猾乎。或曰辛壬癸还上受食之人。太半死亡。必欲责之于其人。则此无异于白骨徵布。今日户还。盖出于不得已也。子何言之过。曰不然。辛壬癸死亡者。诚有之。然太半无田土丐乞之人。无田土则无结卜。无结卜则不得受还上矣。此皆户首里任之所应纳者也。以其户内有死亡之人。故以此为诿。而其实不然也。设有受食而不纳者。其数
用财如流水而无所顾惜。视其积债如浮云之在天。未尝一动其心。原其情状。擢发无惜。而今乃终无捶楚之苦。以掩其罪者何也。君子赏罚之道。不宜如是之舛也。呜呼。有罪而诛之。犹惧法之不立而奸猾之莫惩也。而况置其罪而复免其人所盗之财。以优容之乎。有善而赏之。犹恐化之难行而良善之莫劝也。而况抑其善而使酬他人所负之债。以刻薄之乎。吾知此法一行。还上之多食而不纳者。愈多食而愈不纳矣。其寡食而毕纳者。亦骎骎然怠于纳矣。奸猾之徒。必将弹冠而相庆。幸其计之得售。而绝簿书盗财物。尤无所忌惮也。彼良善之民。亦将圜视而相语。以为国法不足恃。而奸谋谲计。果可以为保家保身之良策也。如此则前日之奸猾。益为奸猾。而今日之良善。又安知不亦后日之奸猾乎。或曰辛壬癸还上受食之人。太半死亡。必欲责之于其人。则此无异于白骨徵布。今日户还。盖出于不得已也。子何言之过。曰不然。辛壬癸死亡者。诚有之。然太半无田土丐乞之人。无田土则无结卜。无结卜则不得受还上矣。此皆户首里任之所应纳者也。以其户内有死亡之人。故以此为诿。而其实不然也。设有受食而不纳者。其数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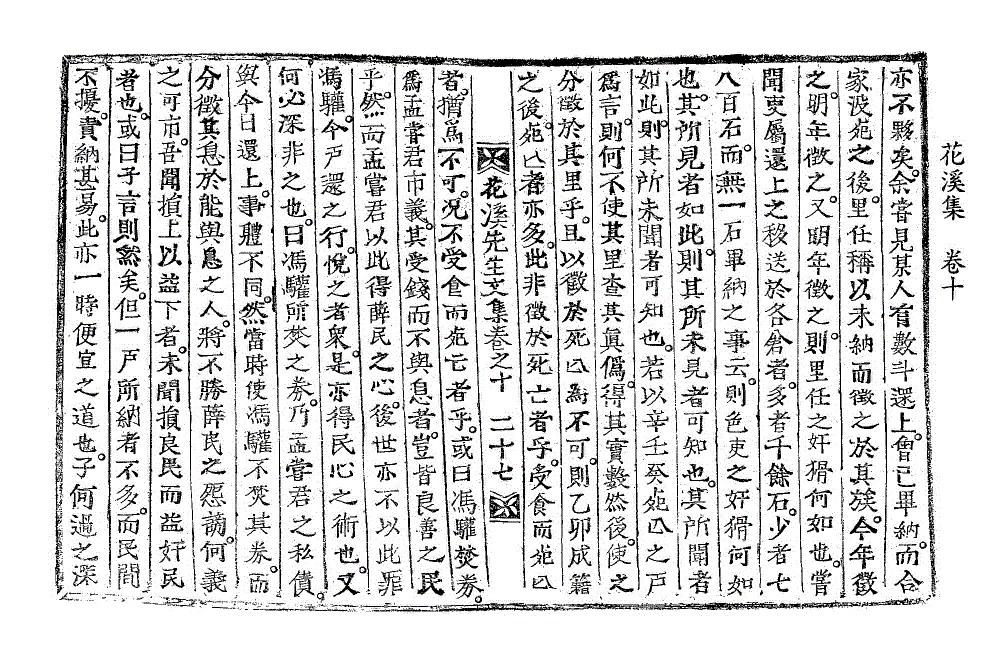 亦不夥矣。余尝见某人有数斗还上。曾已毕纳。而合家没死之后。里任称以未纳而徵之于其族。今年徵之。明年徵之。又明年徵之。则里任之奸猾何如也。尝闻吏属还上之移送于各仓者。多者千馀石。少者七八百石。而无一石毕纳之事云。则色吏之奸猾何如也。其所见者如此。则其所未见者可知也。其所闻者如此。则其所未闻者可知也。若以辛壬癸死亡之户为言。则何不使其里查其真伪。得其实数然后。使之分徵于其里乎。且以徵于死亡为不可。则乙卯成籍之后。死亡者亦多。此非徵于死亡者乎。受食而死亡者。犹为不可。况不受食而死亡者乎。或曰冯驩焚券。为孟尝君市义。其受钱而不与息者。岂皆良善之民乎。然而孟尝君以此得薛民之心。后世亦不以此罪冯驩。今户还之行。悦之者众。是亦得民心之术也。又何必深非之也。曰冯驩所焚之券。乃孟尝君之私债。与今日还上。事体不同。然当时使冯驩不焚其券。而分徵其息于能与息之人。将不胜薛民之怨谤。何义之可市。吾闻损上以益下者。未闻损良民而益奸民者也。或曰子言则然矣。但一户所纳者不多。而民间不扰。责纳甚易。此亦一时便宜之道也。子何过之深
亦不夥矣。余尝见某人有数斗还上。曾已毕纳。而合家没死之后。里任称以未纳而徵之于其族。今年徵之。明年徵之。又明年徵之。则里任之奸猾何如也。尝闻吏属还上之移送于各仓者。多者千馀石。少者七八百石。而无一石毕纳之事云。则色吏之奸猾何如也。其所见者如此。则其所未见者可知也。其所闻者如此。则其所未闻者可知也。若以辛壬癸死亡之户为言。则何不使其里查其真伪。得其实数然后。使之分徵于其里乎。且以徵于死亡为不可。则乙卯成籍之后。死亡者亦多。此非徵于死亡者乎。受食而死亡者。犹为不可。况不受食而死亡者乎。或曰冯驩焚券。为孟尝君市义。其受钱而不与息者。岂皆良善之民乎。然而孟尝君以此得薛民之心。后世亦不以此罪冯驩。今户还之行。悦之者众。是亦得民心之术也。又何必深非之也。曰冯驩所焚之券。乃孟尝君之私债。与今日还上。事体不同。然当时使冯驩不焚其券。而分徵其息于能与息之人。将不胜薛民之怨谤。何义之可市。吾闻损上以益下者。未闻损良民而益奸民者也。或曰子言则然矣。但一户所纳者不多。而民间不扰。责纳甚易。此亦一时便宜之道也。子何过之深花溪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314L 页
 也。曰眼前之疮甚小。而心头之病甚大。吾非惜一户所纳之谷也。所惜者奸猾之日肆而莫之复戢也。纪纲之日紊而莫之复正也。昔宓子贱为单父宰。麦已熟而齐寇将至。父老请使邑民收之。宓子不听。而已寇至。尽失其麦。季孙让之。宓子曰一岁之麦得失。不足为鲁之强弱。而使不耕者得穫。则是使民有幸祸自取之心。其创数年不息。季孙闻而大惭。贾太傅善其言而称之曰明者之塞奸由也早。除乱谋也远。噫今日户还。此奸由之所从生也。乱谋之所从滋也。岂不大可寒心哉。吾故曰奸猾之所利。良善之所害也。小人之所喜。君子之所忧也。
也。曰眼前之疮甚小。而心头之病甚大。吾非惜一户所纳之谷也。所惜者奸猾之日肆而莫之复戢也。纪纲之日紊而莫之复正也。昔宓子贱为单父宰。麦已熟而齐寇将至。父老请使邑民收之。宓子不听。而已寇至。尽失其麦。季孙让之。宓子曰一岁之麦得失。不足为鲁之强弱。而使不耕者得穫。则是使民有幸祸自取之心。其创数年不息。季孙闻而大惭。贾太傅善其言而称之曰明者之塞奸由也早。除乱谋也远。噫今日户还。此奸由之所从生也。乱谋之所从滋也。岂不大可寒心哉。吾故曰奸猾之所利。良善之所害也。小人之所喜。君子之所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