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渼湖集卷之四 第 x 页
渼湖集卷之四
书
书
渼湖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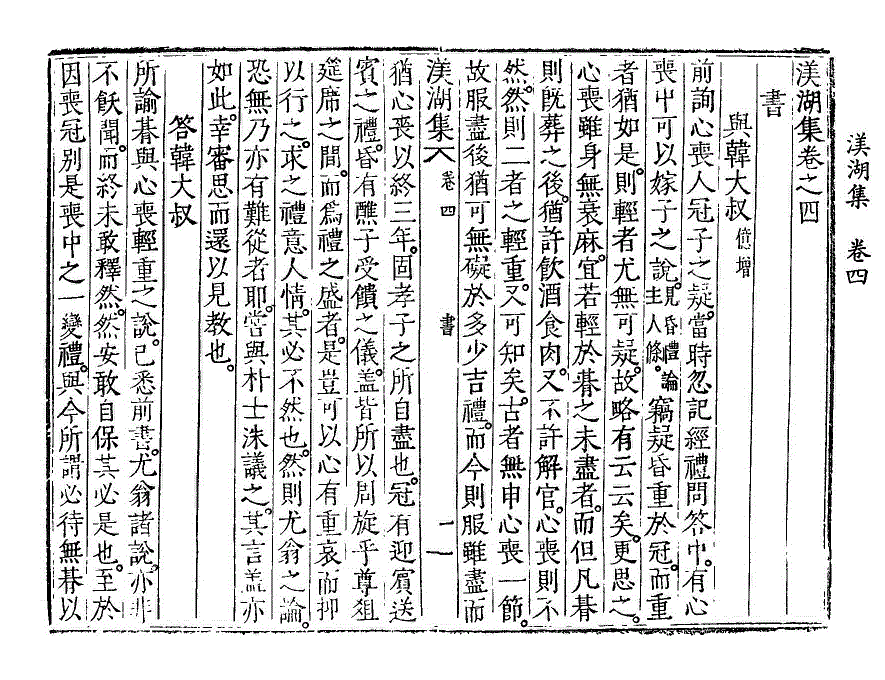 与韩大叔(亿增)
与韩大叔(亿增)前询心丧人冠子之疑。当时忽记经礼问答中。有心丧中可以嫁子之说。(见昏礼论主人条。)窃疑昏重于冠。而重者犹如是。则轻者尤无可疑。故略有云云矣。更思之。心丧虽身无衰麻。宜若轻于期之未尽者。而但凡期则既葬之后。犹许饮酒食肉。又不许解官。心丧则不然。然则二者之轻重。又可知矣。古者无申心丧一节。故服尽后犹可无碍于多少吉礼。而今则服虽尽而犹心丧以终三年。固孝子之所自尽也。冠有迎宾送宾之礼。昏有醮子受馈之仪。盖皆所以周旋乎尊俎筵席之间。而为礼之盛者。是岂可以心有重哀而抑以行之。求之礼意人情。其必不然也。然则尤翁之论。恐无乃亦有难从者耶。尝与朴士洙议之。其言盖亦如此。幸审思而还以见教也。
答韩大叔
所谕期与心丧轻重之说。已悉前书。尤翁诸说。亦非不饫闻。而终未敢释然。然安敢自保其必是也。至于因丧冠别是丧中之一变礼。与今所谓必待无期以
渼湖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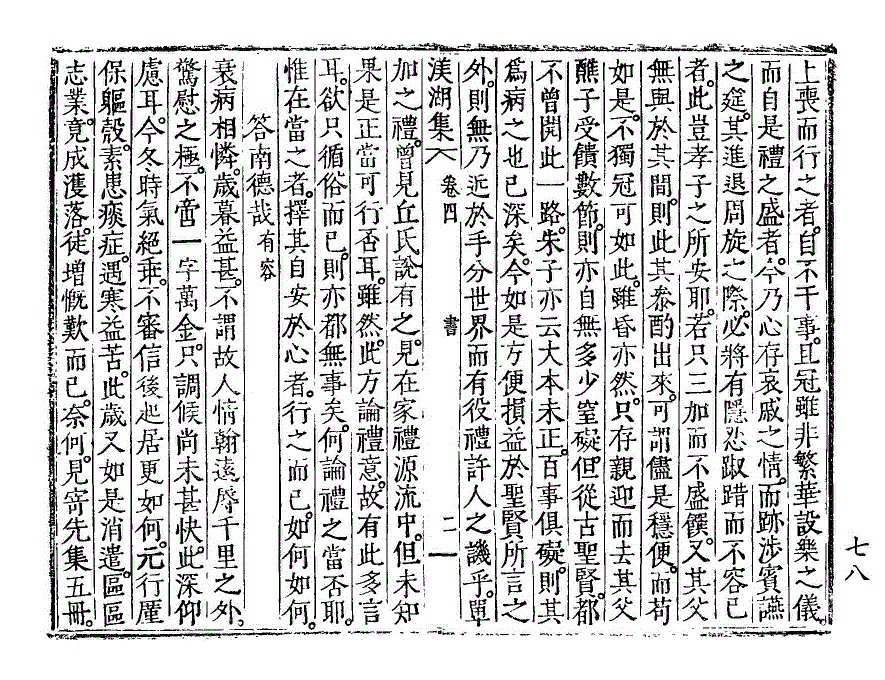 上丧而行之者。自不干事。且冠虽非繁华设乐之仪。而自是礼之盛者。今乃心存哀戚之情。而迹涉宾宴之筵。其进退周旋之际。必将有隐忍踧踖而不容已者。此岂孝子之所安耶。若只三加而不盛馔。又其父无与于其间。则此其参酌出来。可谓尽是稳便。而苟如是。不独冠可如此。虽昏亦然。只存亲迎而去其父醮子受馈数节。则亦自无多少窒碍。但从古圣贤。都不曾开此一路。朱子亦云大本未正。百事俱碍。则其为病之也已深矣。今如是方便损益于圣贤所言之外。则无乃近于手分世界而有役礼许人之讥乎。单加之礼。曾见丘氏说有之。见在家礼源流中。但未知果是正当可行否耳。虽然。此方论礼意。故有此多言耳。欲只循俗而已。则亦都无事矣。何论礼之当否耶。惟在当之者。择其自安于心者。行之而已。如何如何。
上丧而行之者。自不干事。且冠虽非繁华设乐之仪。而自是礼之盛者。今乃心存哀戚之情。而迹涉宾宴之筵。其进退周旋之际。必将有隐忍踧踖而不容已者。此岂孝子之所安耶。若只三加而不盛馔。又其父无与于其间。则此其参酌出来。可谓尽是稳便。而苟如是。不独冠可如此。虽昏亦然。只存亲迎而去其父醮子受馈数节。则亦自无多少窒碍。但从古圣贤。都不曾开此一路。朱子亦云大本未正。百事俱碍。则其为病之也已深矣。今如是方便损益于圣贤所言之外。则无乃近于手分世界而有役礼许人之讥乎。单加之礼。曾见丘氏说有之。见在家礼源流中。但未知果是正当可行否耳。虽然。此方论礼意。故有此多言耳。欲只循俗而已。则亦都无事矣。何论礼之当否耶。惟在当之者。择其自安于心者。行之而已。如何如何。答南德哉(有容)
衰病相怜。岁暮益甚。不谓故人情翰远辱千里之外。惊慰之极。不啻一字万金。只调候尚未甚快。此深仰虑耳。今冬时气绝乖。不审信后起居更如何。元行廑保躯壳。素患痰症。遇寒益苦。此岁又如是消遣。区区志业。竟成濩落。徒增慨叹而已。奈何。见寄先集五册。
渼湖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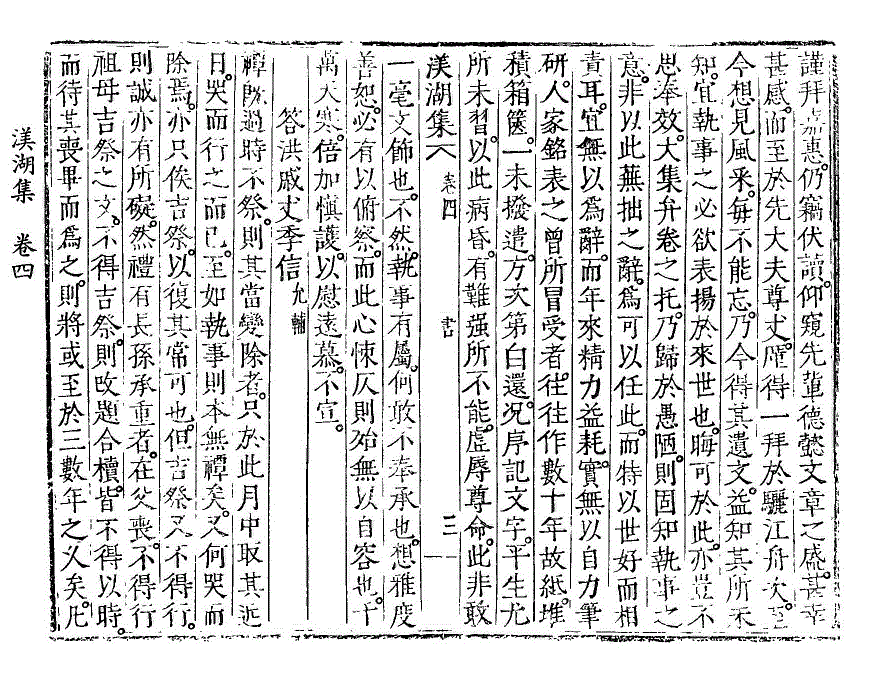 谨拜嘉惠。仍窃伏读。仰窥先辈德懿文章之盛。甚幸甚感。而至于先大夫尊丈。廑得一拜于骊江舟次。至今想见风采。每不能忘。乃今得其遗文。益知其所未知。宜执事之必欲表扬于来世也。晦可于此。亦岂不思奉效。大集弁卷之托。乃归于愚陋。则固知执事之意。非以此芜拙之辞。为可以任此。而特以世好而相责耳。宜无以为辞。而年来精力益耗。实无以自力笔研。人家铭表之曾所冒受者。往往作数十年故纸。堆积箱箧。一未拨遣。方次第白还。况序记文字。平生尤所未习。以此病昏。有难强所不能。虚辱尊命。此非敢一毫文饰也。不然。执事有属。何敢不奉承也。想雅度善恕。必有以俯察。而此心悚仄则殆无以自容也。千万天寒。倍加慎护。以慰远慕。不宣。
谨拜嘉惠。仍窃伏读。仰窥先辈德懿文章之盛。甚幸甚感。而至于先大夫尊丈。廑得一拜于骊江舟次。至今想见风采。每不能忘。乃今得其遗文。益知其所未知。宜执事之必欲表扬于来世也。晦可于此。亦岂不思奉效。大集弁卷之托。乃归于愚陋。则固知执事之意。非以此芜拙之辞。为可以任此。而特以世好而相责耳。宜无以为辞。而年来精力益耗。实无以自力笔研。人家铭表之曾所冒受者。往往作数十年故纸。堆积箱箧。一未拨遣。方次第白还。况序记文字。平生尤所未习。以此病昏。有难强所不能。虚辱尊命。此非敢一毫文饰也。不然。执事有属。何敢不奉承也。想雅度善恕。必有以俯察。而此心悚仄则殆无以自容也。千万天寒。倍加慎护。以慰远慕。不宣。答洪戚丈季信(允辅)
禫既过时不祭。则其当变除者。只于此月中取其近日。哭而行之而已。至如执事则本无禫矣。又何哭而除焉。亦只俟吉祭。以复其常可也。但吉祭又不得行。则诚亦有所碍。然礼有长孙承重者。在父丧。不得行祖母吉祭之文。不得吉祭。则改题合椟。皆不得以时。而待其丧毕而为之。则将或至于三数年之久矣。凡
渼湖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支子之当变除者。以其不及改题合椟。而又至于三数年。而犹不得免丧。岂理欤。今贤咸之病。固未知如何。然人之有疾。其迟速固不可期。而设或有累月经岁而不已。则诸子又因是而皆不得免丧。终为过矣。夫先王之为礼也。丧至于二十五月则既毕矣。犹待夫禫吉然后。即乎纯吉者。以其馀哀之未忘。而又为之少引数月。以自尽而已。至此则抑可以止矣。故礼云是月禫徙月乐。又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至孔子之所自为也。又既祥五日而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此所谓圣人之中制也。贤者之所俯而就之。而不得过。不肖者之所企而及之。而不敢不至者也。今为长孙之有故。而又引而至于累月经岁而莫之变。则岂非所谓过欤。故愚意以为今日之事。执事于来月当祭之日。可以复常如礼。而至若合椟之节。待贤咸粗安。别为祭而行之。似无不可者矣。
支子之当变除者。以其不及改题合椟。而又至于三数年。而犹不得免丧。岂理欤。今贤咸之病。固未知如何。然人之有疾。其迟速固不可期。而设或有累月经岁而不已。则诸子又因是而皆不得免丧。终为过矣。夫先王之为礼也。丧至于二十五月则既毕矣。犹待夫禫吉然后。即乎纯吉者。以其馀哀之未忘。而又为之少引数月。以自尽而已。至此则抑可以止矣。故礼云是月禫徙月乐。又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至孔子之所自为也。又既祥五日而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此所谓圣人之中制也。贤者之所俯而就之。而不得过。不肖者之所企而及之。而不敢不至者也。今为长孙之有故。而又引而至于累月经岁而莫之变。则岂非所谓过欤。故愚意以为今日之事。执事于来月当祭之日。可以复常如礼。而至若合椟之节。待贤咸粗安。别为祭而行之。似无不可者矣。答洪戚丈季信
吉祭之摄行。是谓主祭者身有重病。至于累月经岁。而改题合椟之事。皆不可以许久延拖。则不得已而或可如此者也。如今贤咸可以起动于数月之内。则自可以躬行者。不在所论也。
答洪戚丈季信
行职赠职先后之说。曾于尤翁集似见之。而今考得不出。然朱夫子于其告考妣文。有曰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赠通义大夫府君云云。此先行后赠之一大明證。恐无待他说矣。如何如何。此在大全八十九卷二十一板矣。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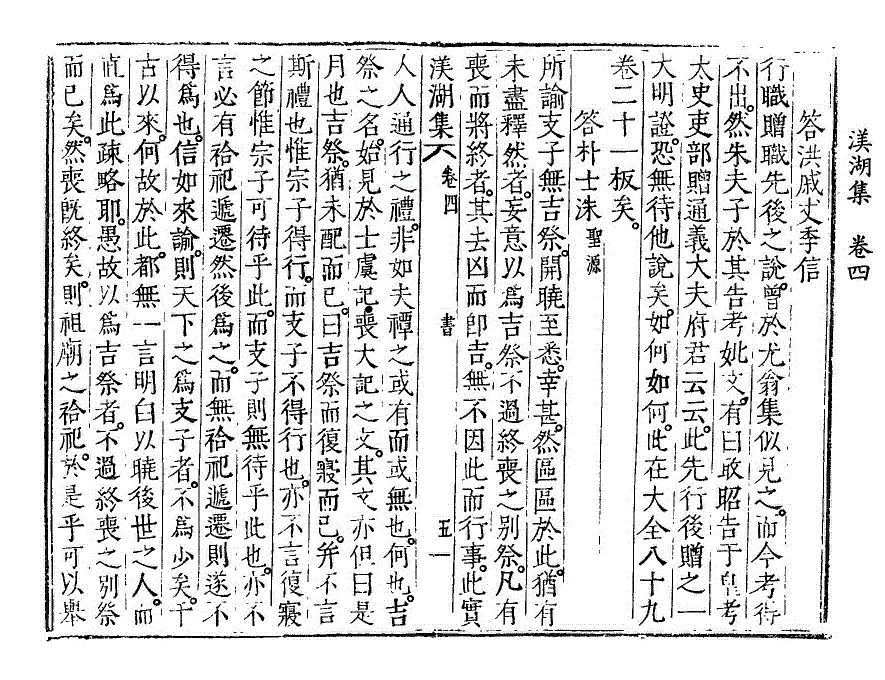 答朴士洙(圣源)
答朴士洙(圣源)所谕支子无吉祭。开晓至悉。幸甚。然区区于此。犹有未尽释然者。妄意以为吉祭不过终丧之别祭。凡有丧而将终者。其去凶而即吉。无不因此而行事。此实人人通行之礼。非如夫禫之或有而或无也。何也。吉祭之名。始见于士虞记,丧大记之文。其文亦但曰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而已。曰吉祭而复寝而已。并不言斯礼也惟宗子得行。而支子不得行也。亦不言复寝之节。惟宗子可待乎此。而支子则无待乎此也。亦不言必有祫祀递迁然后为之。而无祫祀递迁则遂不得为也。信如来谕。则天下之为支子者。不为少矣。千古以来。何故于此。都无一言明白以晓后世之人。而直为此疏略耶。愚故以为吉祭者。不过终丧之别祭而已矣。然丧既终矣。则祖庙之祫祀。于是乎可以举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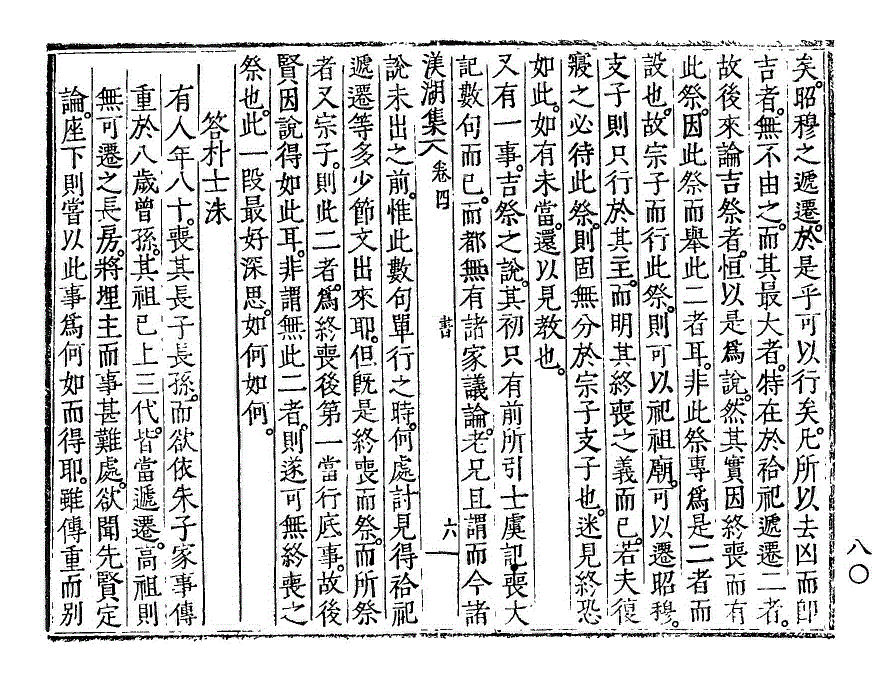 矣。昭穆之递迁。于是乎可以行矣。凡所以去凶而即吉者。无不由之。而其最大者。特在于祫祀递迁二者。故后来论吉祭者。恒以是为说。然其实因终丧而有此祭。因此祭而举此二者耳。非此祭专为是二者而设也。故宗子而行此祭。则可以祀祖庙。可以迁昭穆。支子则只行于其主。而明其终丧之义而已。若夫复寝之必待此祭。则固无分于宗子支子也。迷见终恐如此。如有未当。还以见教也。
矣。昭穆之递迁。于是乎可以行矣。凡所以去凶而即吉者。无不由之。而其最大者。特在于祫祀递迁二者。故后来论吉祭者。恒以是为说。然其实因终丧而有此祭。因此祭而举此二者耳。非此祭专为是二者而设也。故宗子而行此祭。则可以祀祖庙。可以迁昭穆。支子则只行于其主。而明其终丧之义而已。若夫复寝之必待此祭。则固无分于宗子支子也。迷见终恐如此。如有未当。还以见教也。又有一事。吉祭之说。其初只有前所引士虞记,丧大记数句而已。而都无有诸家议论。老兄且谓而今诸说未出之前。惟此数句单行之时。何处讨见得祫祀递迁等多少节文出来耶。但既是终丧而祭。而所祭者又宗子。则此二者。为终丧后第一当行底事。故后贤因说得如此耳。非谓无此二者。则遂可无终丧之祭也。此一段最好深思。如何如何。
答朴士洙
有人年八十。丧其长子长孙。而欲依朱子家事传重于八岁曾孙。其祖已上三代。皆当递迁。高祖则无可迁之长房。将埋主而事甚难处。欲闻先贤定论。座下则尝以此事为何如而得耶。虽传重而别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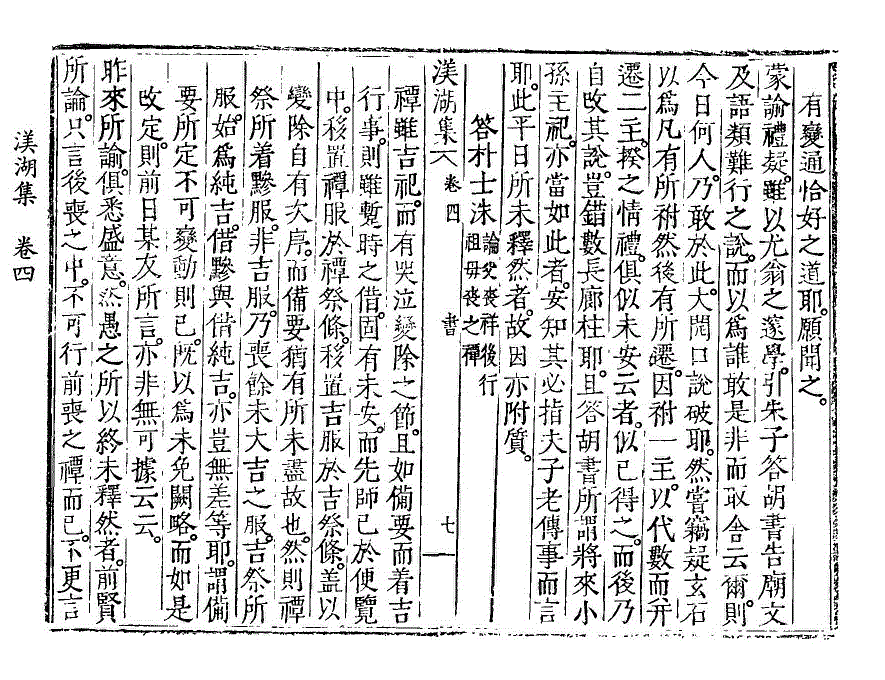 有变通恰好之道耶。愿闻之。
有变通恰好之道耶。愿闻之。蒙谕礼疑。虽以尤翁之邃学。引朱子答胡书告庙文及语类难行之说。而以为谁敢是非而取舍云尔。则今日何人。乃敢于此。大开口说破耶。然尝窃疑玄石以为凡有所祔然后有所迁。因祔一主。以代数而并迁二主。揆之情礼。俱似未安云者。似已得之。而后乃自改其说。岂错数长廊柱耶。且答胡书所谓将来小孙主祀。亦当如此者。安知其必指夫子老传事而言耶。此平日所未释然者。故因亦附质。
答朴士洙(论父丧祥后行祖母丧之禫)
禫虽吉祀。而有哭泣变除之节。且如备要而着吉行事。则虽暂时之借。固有未安。而先师已于便览中。移置禫服于禫祭条。移置吉服于吉祭条。盖以变除自有次序。而备要犹有所未尽故也。然则禫祭所着黪服。非吉服。乃丧馀未大吉之服。吉祭所服。始为纯吉。借黪与借纯吉。亦岂无差等耶。谓备要所定不可变动则已。既以为未免阙略。而如是改定。则前日某友所言。亦非无可据云云。
昨来所谕。俱悉盛意。然愚之所以终未释然者。前贤所论。只言后丧之中。不可行前丧之禫而已。不更言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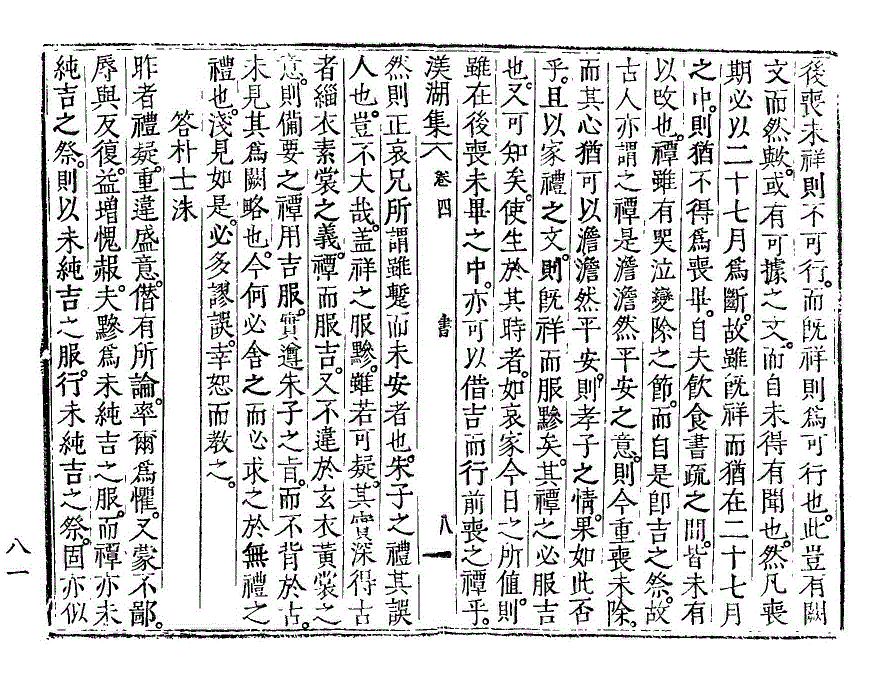 后丧未祥则不可行。而既祥则为可行也。此岂有阙文而然欤。或有可据之文。而自未得有闻也。然凡丧期必以二十七月为断。故虽既祥而犹在二十七月之中。则犹不得为丧毕。自夫饮食书疏之间。皆未有以改也。禫虽有哭泣变除之节。而自是即吉之祭。故古人亦谓之禫是澹澹然平安之意。则今重丧未除。而其心犹可以澹澹然平安。则孝子之情。果如此否乎。且以家礼之文。则既祥而服黪矣。其禫之必服吉也。又可知矣。使生于其时者。如哀家今日之所值。则虽在后丧未毕之中。亦可以借吉而行前丧之禫乎。然则正哀兄所谓虽暂而未安者也。朱子之礼其误人也。岂不大哉。盖祥之服黪。虽若可疑。其实深得古者缁衣素裳之义。禫而服吉。又不违于玄衣黄裳之意。则备要之禫用吉服。实遵朱子之旨。而不背于古。未见其为阙略也。今何必舍之而必求之于无礼之礼也。浅见如是。必多谬误。幸恕而教之。
后丧未祥则不可行。而既祥则为可行也。此岂有阙文而然欤。或有可据之文。而自未得有闻也。然凡丧期必以二十七月为断。故虽既祥而犹在二十七月之中。则犹不得为丧毕。自夫饮食书疏之间。皆未有以改也。禫虽有哭泣变除之节。而自是即吉之祭。故古人亦谓之禫是澹澹然平安之意。则今重丧未除。而其心犹可以澹澹然平安。则孝子之情。果如此否乎。且以家礼之文。则既祥而服黪矣。其禫之必服吉也。又可知矣。使生于其时者。如哀家今日之所值。则虽在后丧未毕之中。亦可以借吉而行前丧之禫乎。然则正哀兄所谓虽暂而未安者也。朱子之礼其误人也。岂不大哉。盖祥之服黪。虽若可疑。其实深得古者缁衣素裳之义。禫而服吉。又不违于玄衣黄裳之意。则备要之禫用吉服。实遵朱子之旨。而不背于古。未见其为阙略也。今何必舍之而必求之于无礼之礼也。浅见如是。必多谬误。幸恕而教之。答朴士洙
昨者礼疑。重违盛意。僭有所论。率尔为惧。又蒙不鄙。辱与反复。益增愧赧。夫黪为未纯吉之服。而禫亦未纯吉之祭。则以未纯吉之服。行未纯吉之祭。固亦似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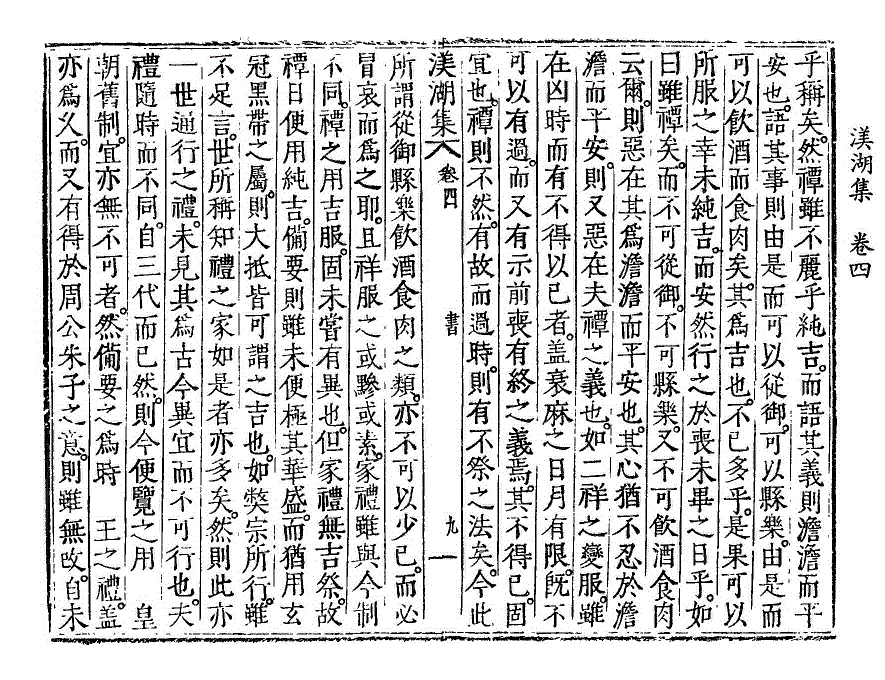 乎称矣。然禫虽不丽乎纯吉。而语其义则澹澹而平安也。语其事则由是而可以从御。可以县乐。由是而可以饮酒而食肉矣。其为吉也。不已多乎。是果可以所服之幸未纯吉。而安然行之于丧未毕之日乎。如曰虽禫矣。而不可从御。不可县乐。又不可饮酒食肉云尔。则恶在其为澹澹而平安也。其心犹不忍于澹澹而平安。则又恶在夫禫之义也。如二祥之变服。虽在凶时而有不得以已者。盖衰麻之日月有限。既不可以有过。而又有示前丧有终之义焉。其不得已。固宜也。禫则不然。有故而过时。则有不祭之法矣。今此所谓从御县乐饮酒食肉之类。亦不可以少已。而必冒哀而为之耶。且祥服之或黪或素。家礼虽与今制不同。禫之用吉服。固未尝有异也。但家礼无吉祭。故禫日便用纯吉。备要则虽未便极其华盛。而犹用玄冠黑带之属。则大抵皆可谓之吉也。如弊宗所行。虽不足言。世所称知礼之家如是者亦多矣。然则此亦一世通行之礼。未见其为古今异宜而不可行也。夫礼随时而不同。自三代而已然。则今便览之用 皇朝旧制。宜亦无不可者。然备要之为时 王之礼。盖亦为久。而又有得于周公朱子之意。则虽无改。自未
乎称矣。然禫虽不丽乎纯吉。而语其义则澹澹而平安也。语其事则由是而可以从御。可以县乐。由是而可以饮酒而食肉矣。其为吉也。不已多乎。是果可以所服之幸未纯吉。而安然行之于丧未毕之日乎。如曰虽禫矣。而不可从御。不可县乐。又不可饮酒食肉云尔。则恶在其为澹澹而平安也。其心犹不忍于澹澹而平安。则又恶在夫禫之义也。如二祥之变服。虽在凶时而有不得以已者。盖衰麻之日月有限。既不可以有过。而又有示前丧有终之义焉。其不得已。固宜也。禫则不然。有故而过时。则有不祭之法矣。今此所谓从御县乐饮酒食肉之类。亦不可以少已。而必冒哀而为之耶。且祥服之或黪或素。家礼虽与今制不同。禫之用吉服。固未尝有异也。但家礼无吉祭。故禫日便用纯吉。备要则虽未便极其华盛。而犹用玄冠黑带之属。则大抵皆可谓之吉也。如弊宗所行。虽不足言。世所称知礼之家如是者亦多矣。然则此亦一世通行之礼。未见其为古今异宜而不可行也。夫礼随时而不同。自三代而已然。则今便览之用 皇朝旧制。宜亦无不可者。然备要之为时 王之礼。盖亦为久。而又有得于周公朱子之意。则虽无改。自未渼湖集卷之四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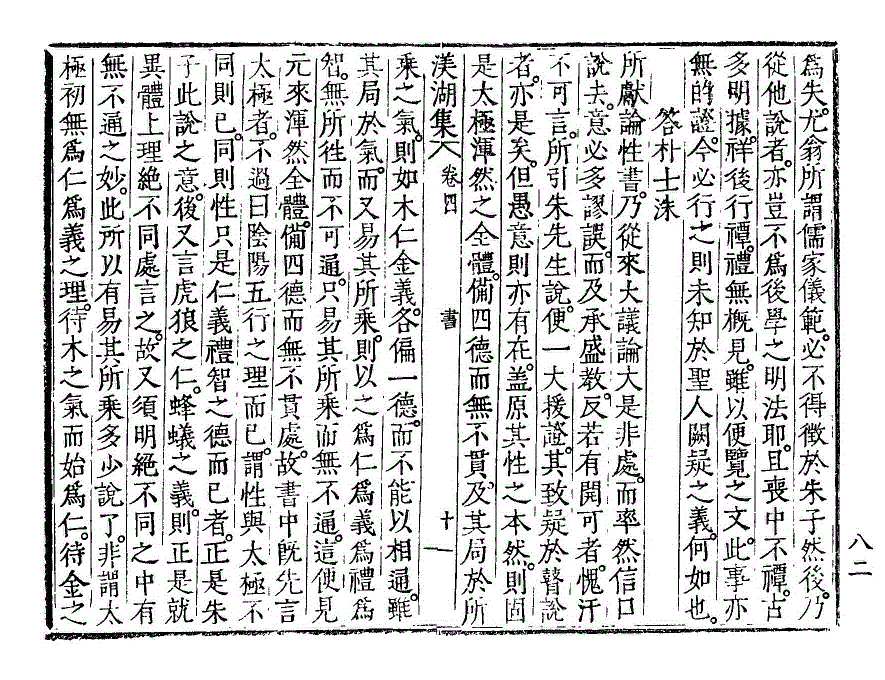 为失。尤翁所谓儒家仪范。必不得徵于朱子然后。乃从他说者。亦岂不为后学之明法耶。且丧中不禫。古多明据。祥后行禫。礼无概见。虽以便览之文。此事亦无的證。今必行之则未知于圣人阙疑之义。何如也。
为失。尤翁所谓儒家仪范。必不得徵于朱子然后。乃从他说者。亦岂不为后学之明法耶。且丧中不禫。古多明据。祥后行禫。礼无概见。虽以便览之文。此事亦无的證。今必行之则未知于圣人阙疑之义。何如也。答朴士洙
所献论性书。乃从来大议论大是非处。而率然信口说去。意必多谬误。而及承盛教。反若有开可者。愧汗不可言。所引朱先生说。便一大援證。其致疑于瞽说者。亦是矣。但愚意则亦有在。盖原其性之本然。则固是太极浑然之全体。备四德而无不贯。及其局于所乘之气。则如木仁金义。各偏一德。而不能以相通。虽其局于气。而又易其所乘。则以之为仁为义为礼为智。无所往而不可通。只易其所乘而无不通。这便见元来浑然全体。备四德而无不贯处。故书中既先言太极者。不过曰阴阳五行之理而已。谓性与太极不同则已。同则性只是仁义礼智之德而已者。正是朱子此说之意。后又言虎狼之仁。蜂蚁之义。则正是就异体上理绝不同处言之。故又须明绝不同之中有无不通之妙。此所以有易其所乘多少说了。非谓太极初无为仁为义之理。待木之气而始为仁。待金之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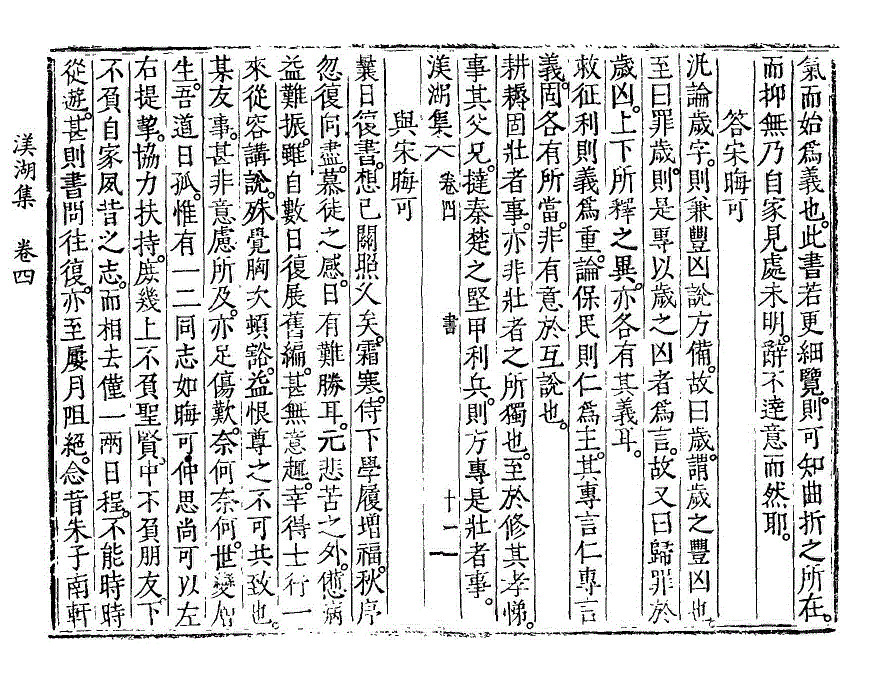 气而始为义也。此书若更细览。则可知曲折之所在。而抑无乃自家见处未明。辞不达意而然耶。
气而始为义也。此书若更细览。则可知曲折之所在。而抑无乃自家见处未明。辞不达意而然耶。答宋晦可
汎论岁字。则兼丰凶说方备。故曰岁。谓岁之丰凶也。至曰罪岁。则是专以岁之凶者为言。故又曰归罪于岁凶。上下所释之异。亦各有其义耳。
救征利则义为重。论保民则仁为主。其专言仁专言义。固各有所当。非有意于互说也。
耕耨固壮者事。亦非壮者之所独也。至于修其孝悌。事其父兄。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方专是壮者事。
与宋晦可
曩日复书。想已关照久矣。霜寒。侍下学履增福。秋序忽复向尽。慕徒之感。日有难胜耳。元悲苦之外。惫病益难振。虽自数日复展旧编。甚无意趣。幸得士行一来从容讲说。殊觉胸次顿豁。益恨尊之不可共致也。某友事。甚非意虑所及。亦足伤叹。奈何奈何。世变层生。吾道日孤。惟有一二同志如晦可,仲思尚可以左右提挈。协力扶持。庶几上不负圣贤。中不负朋友。下不负自家夙昔之志。而相去仅一两日程。不能时时从游。甚则书问往复。亦至屡月阻绝。念昔朱子南轩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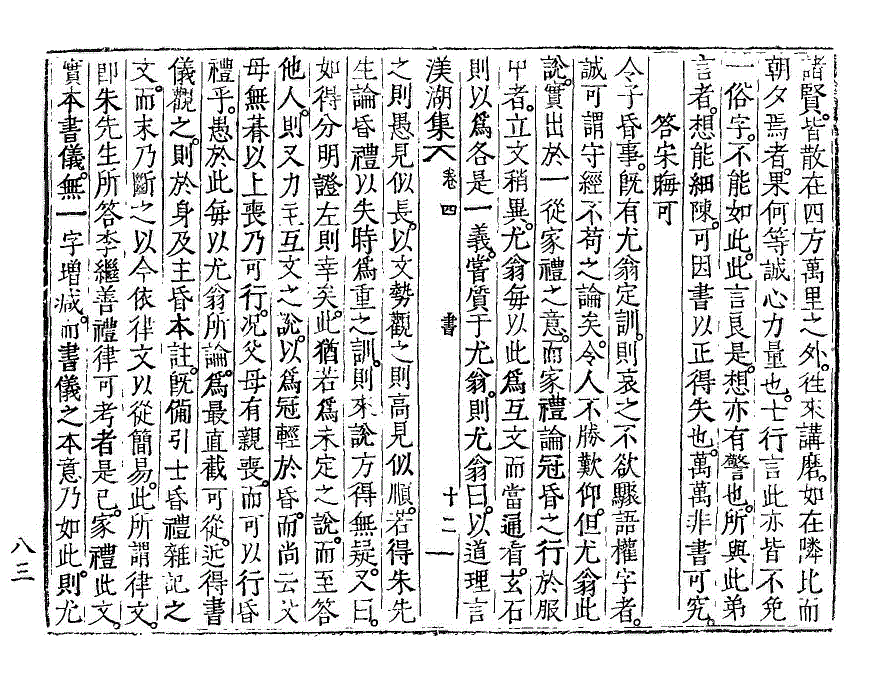 诸贤。皆散在四方万里之外。往来讲磨。如在邻比而朝夕焉者。果何等诚心力量也。士行言此亦皆不免一俗字。不能如此。此言良是。想亦有警也。所与此弟言者。想能细陈。可因书以正得失也。万万非书可究。
诸贤。皆散在四方万里之外。往来讲磨。如在邻比而朝夕焉者。果何等诚心力量也。士行言此亦皆不免一俗字。不能如此。此言良是。想亦有警也。所与此弟言者。想能细陈。可因书以正得失也。万万非书可究。答宋晦可
令子昏事。既有尤翁定训。则哀之不欲骤语权字者。诚可谓守经不苟之论矣。令人不胜叹仰。但尤翁此说。实出于一从家礼之意。而家礼论冠昏之行于服中者。立文稍异。尤翁每以此为互文而当通看。玄石则以为各是一义。尝质于尤翁。则尤翁曰。以道理言之则愚见似长。以文势观之则高见似顺。若得朱先生论昏礼以失时为重之训。则来说方得无疑。又曰。如得分明證左则幸矣。此犹若为未定之说。而至答他人。则又力主互文之说。以为冠轻于昏。而尚云父母无期以上丧乃可行。况父母有亲丧。而可以行昏礼乎。愚于此每以尤翁所论。为最直截可从。近得书仪观之。则于身及主昏本注。既备引士昏礼杂记之文。而末乃断之以今依律文以从简易。此所谓律文。即朱先生所答李继善礼律可考者是已。家礼此文。实本书仪。无一字增减。而书仪之本意乃如此。则尤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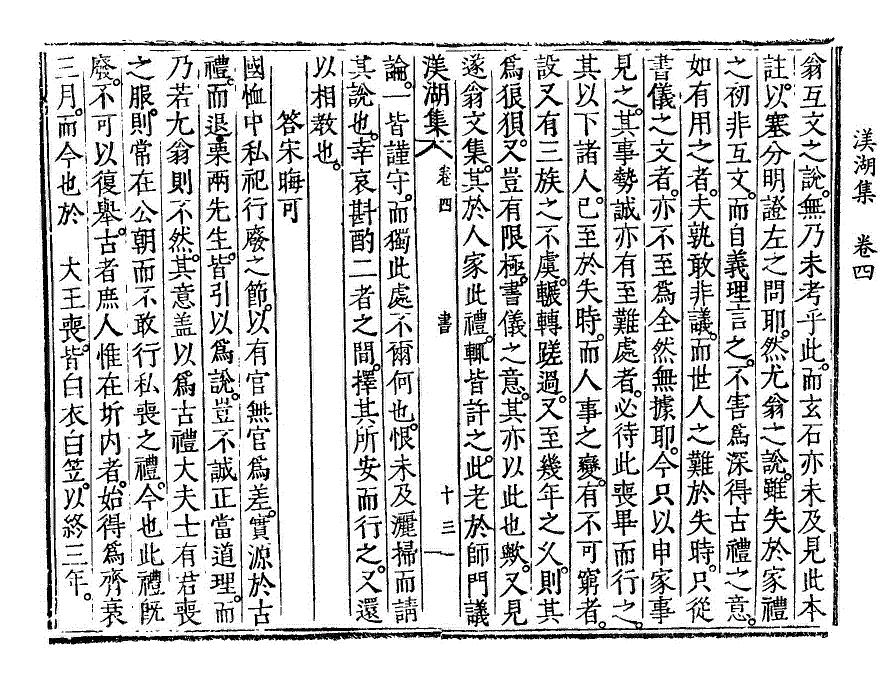 翁互文之说。无乃未考乎此。而玄石亦未及见此本注。以塞分明證左之问耶。然尤翁之说。虽失于家礼之初非互文。而自义理言之。不害为深得古礼之意。如有用之者。夫孰敢非议。而世人之难于失时。只从书仪之文者。亦不至为全然无据耶。今只以申家事见之。其事势诚亦有至难处者。必待此丧毕而行之。其以下诸人。已至于失时。而人事之变。有不可穷者。设又有三族之不虞。辗转蹉过。又至几年之久。则其为狼狈。又岂有限极。书仪之意。其亦以此也欤。又见遂翁文集。其于人家此礼。辄皆许之。此老于师门议论。一皆谨守。而独此处不尔何也。恨未及洒扫而请其说也。幸哀斟酌二者之间。择其所安而行之。又还以相教也。
翁互文之说。无乃未考乎此。而玄石亦未及见此本注。以塞分明證左之问耶。然尤翁之说。虽失于家礼之初非互文。而自义理言之。不害为深得古礼之意。如有用之者。夫孰敢非议。而世人之难于失时。只从书仪之文者。亦不至为全然无据耶。今只以申家事见之。其事势诚亦有至难处者。必待此丧毕而行之。其以下诸人。已至于失时。而人事之变。有不可穷者。设又有三族之不虞。辗转蹉过。又至几年之久。则其为狼狈。又岂有限极。书仪之意。其亦以此也欤。又见遂翁文集。其于人家此礼。辄皆许之。此老于师门议论。一皆谨守。而独此处不尔何也。恨未及洒扫而请其说也。幸哀斟酌二者之间。择其所安而行之。又还以相教也。答宋晦可
国恤中私祀行废之节。以有官无官为差。实源于古礼。而退,栗两先生。皆引以为说。岂不诚正当道理。而乃若尤翁则不然。其意盖以为古礼大夫士有君丧之服。则常在公朝而不敢行私丧之礼。今也此礼既废。不可以复举。古者庶人惟在圻内者。始得为齐衰三月。而今也于 大王丧。皆白衣白笠。以终三年。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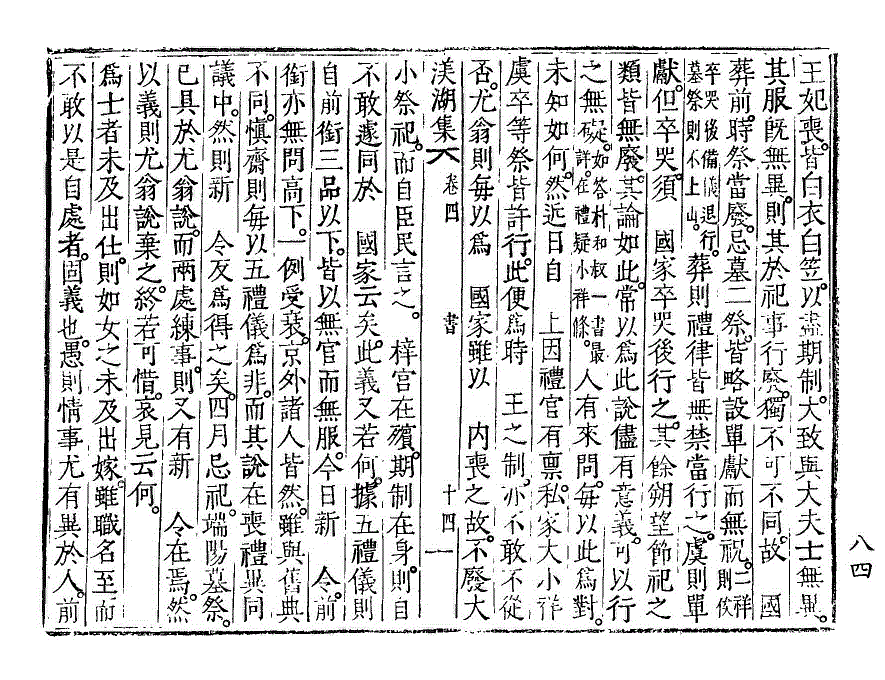 王妃丧。皆白衣白笠。以尽期制。大致与大夫士无异。其服既无异。则其于祀事行废。独不可不同。故 国葬前。时祭当废。忌墓二祭。皆略设单献而无祝。(二祥则俟卒哭后备仪退行。墓祭则不上山。)葬则礼律皆无禁当行之。虞则单献。但卒哭。须 国家卒哭后行之。其馀朔望节祀之类皆无废。其论如此。常以为此说尽有意义。可以行之无碍。(如答朴和叔一书最详。在礼疑小祥条。)人有来问。每以此为对。未知如何。然近日自 上因礼官有禀。私家大小祥虞卒等祭皆许行。此便为时 王之制。亦不敢不从否。尤翁则每以为 国家虽以 内丧之故。不废大小祭祀。而自臣民言之。 梓宫在殡。期制在身。则自不敢遽同于 国家云矣。此义又若何。据五礼仪则自前衔三品以下。皆以无官而无服。今日新 令。前衔亦无问高下。一例受衰。京外诸人皆然。虽与旧典不同。慎斋则每以五礼仪为非。而其说在丧礼异同议中。然则新 令反为得之矣。四月忌祀。端阳墓祭。已具于尤翁说。而两处练事。则又有新 令在焉。然以义则尤翁说弃之。终若可惜。哀见云何。
王妃丧。皆白衣白笠。以尽期制。大致与大夫士无异。其服既无异。则其于祀事行废。独不可不同。故 国葬前。时祭当废。忌墓二祭。皆略设单献而无祝。(二祥则俟卒哭后备仪退行。墓祭则不上山。)葬则礼律皆无禁当行之。虞则单献。但卒哭。须 国家卒哭后行之。其馀朔望节祀之类皆无废。其论如此。常以为此说尽有意义。可以行之无碍。(如答朴和叔一书最详。在礼疑小祥条。)人有来问。每以此为对。未知如何。然近日自 上因礼官有禀。私家大小祥虞卒等祭皆许行。此便为时 王之制。亦不敢不从否。尤翁则每以为 国家虽以 内丧之故。不废大小祭祀。而自臣民言之。 梓宫在殡。期制在身。则自不敢遽同于 国家云矣。此义又若何。据五礼仪则自前衔三品以下。皆以无官而无服。今日新 令。前衔亦无问高下。一例受衰。京外诸人皆然。虽与旧典不同。慎斋则每以五礼仪为非。而其说在丧礼异同议中。然则新 令反为得之矣。四月忌祀。端阳墓祭。已具于尤翁说。而两处练事。则又有新 令在焉。然以义则尤翁说弃之。终若可惜。哀见云何。为士者未及出仕。则如女之未及出嫁。虽职名至而不敢以是自处者。固义也。愚则情事尤有异于人。前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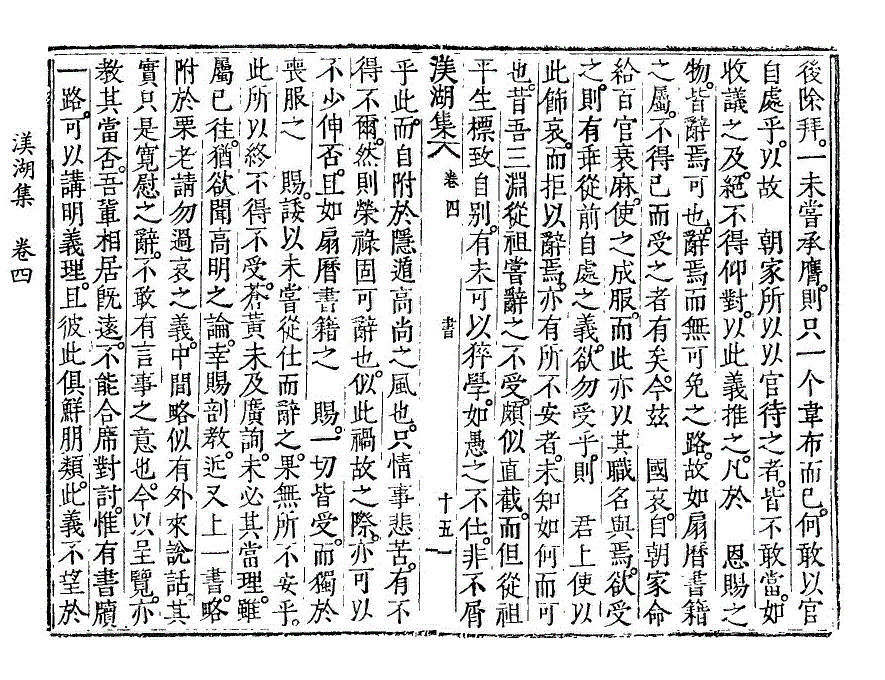 后除拜。一未尝承膺。则只一个韦布而已。何敢以官自处乎。以故 朝家所以以官待之者。皆不敢当。如收议之及。绝不得仰对。以此义推之。凡于 恩赐之物。皆辞焉可也。辞焉而无可免之路。故如扇历书籍之属。不得已而受之者有矣。今玆 国哀。自朝家命给百官衰麻。使之成服。而此亦以其职名与焉。欲受之。则有乖从前自处之义。欲勿受乎。则 君上使以此饰哀。而拒以辞焉。亦有所不安者。未知如何而可也。昔吾三渊从祖尝辞之不受。颇似直截。而但从祖平生标致自别。有未可以猝学。如愚之不仕。非不屑乎此。而自附于隐遁高尚之风也。只情事悲苦。有不得不尔。然则荣禄固可辞也。似此祸故之际。亦可以不少伸否。且如扇历书籍之 赐。一切皆受。而独于丧服之 赐。诿以未尝从仕而辞之。果无所不安乎。此所以终不得不受。苍黄未及广询。未必其当理。虽属已往。犹欲闻高明之论。幸赐剖教。近又上一书。略附于栗老请勿过哀之义。中间略似有外来说话。其实只是宽慰之辞。不敢有言事之意也。今以呈览。亦教其当否。吾辈相居既远。不能合席对讨。惟有书牍一路。可以讲明义理。且彼此俱鲜朋类。此义不望于
后除拜。一未尝承膺。则只一个韦布而已。何敢以官自处乎。以故 朝家所以以官待之者。皆不敢当。如收议之及。绝不得仰对。以此义推之。凡于 恩赐之物。皆辞焉可也。辞焉而无可免之路。故如扇历书籍之属。不得已而受之者有矣。今玆 国哀。自朝家命给百官衰麻。使之成服。而此亦以其职名与焉。欲受之。则有乖从前自处之义。欲勿受乎。则 君上使以此饰哀。而拒以辞焉。亦有所不安者。未知如何而可也。昔吾三渊从祖尝辞之不受。颇似直截。而但从祖平生标致自别。有未可以猝学。如愚之不仕。非不屑乎此。而自附于隐遁高尚之风也。只情事悲苦。有不得不尔。然则荣禄固可辞也。似此祸故之际。亦可以不少伸否。且如扇历书籍之 赐。一切皆受。而独于丧服之 赐。诿以未尝从仕而辞之。果无所不安乎。此所以终不得不受。苍黄未及广询。未必其当理。虽属已往。犹欲闻高明之论。幸赐剖教。近又上一书。略附于栗老请勿过哀之义。中间略似有外来说话。其实只是宽慰之辞。不敢有言事之意也。今以呈览。亦教其当否。吾辈相居既远。不能合席对讨。惟有书牍一路。可以讲明义理。且彼此俱鲜朋类。此义不望于渼湖集卷之四 第 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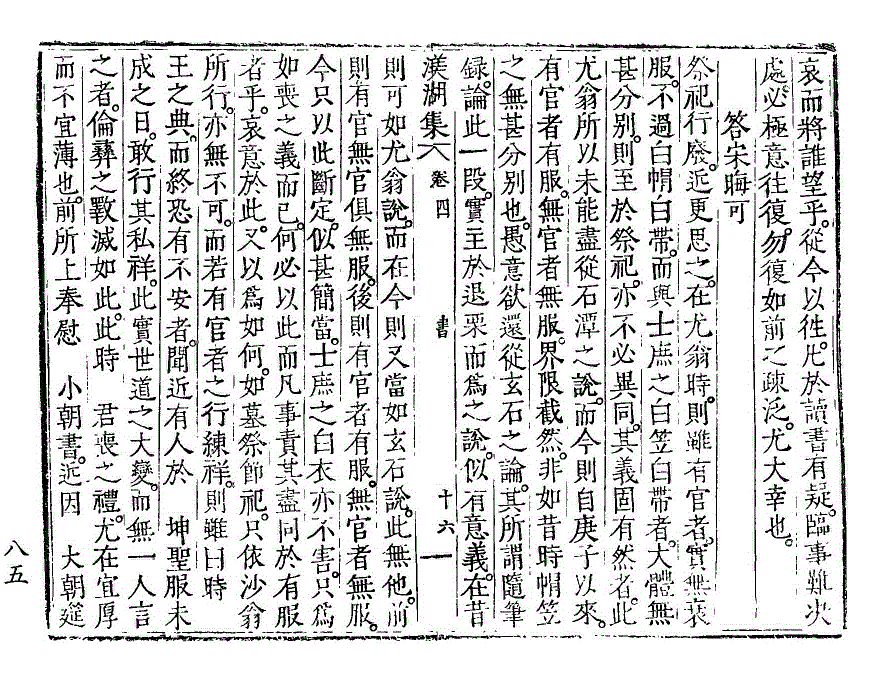 哀而将谁望乎。从今以往。凡于读书有疑。临事难决处。必极意往复。勿复如前之疏泛。尤大幸也。
哀而将谁望乎。从今以往。凡于读书有疑。临事难决处。必极意往复。勿复如前之疏泛。尤大幸也。答宋晦可
祭祀行废。近更思之。在尤翁时。则虽有官者。实无衰服。不过白帽白带。而与士庶之白笠白带者。大体无甚分别。则至于祭祀。亦不必异同。其义固有然者。此尤翁所以未能尽从石潭之说。而今则自庚子以来。有官者有服。无官者无服。界限截然。非如昔时帽笠之无甚分别也。愚意欲还从玄石之论。其所谓随笔录。论此一段。实主于退栗而为之说。似有意义。在昔则可如尤翁说。而在今则又当如玄石说。此无他。前则有官无官俱无服。后则有官者有服。无官者无服。今只以此断定。似甚简当。士庶之白衣亦不害。只为如丧之义而已。何必以此而凡事责其尽同于有服者乎。哀意于此。又以为如何。如墓祭节祀。只依沙翁所行。亦无不可。而若有官者之行练祥。则虽曰时 王之典。而终恐有不安者。闻近有人于 坤圣服未成之日。敢行其私祥。此实世道之大变。而无一人言之者。伦彝之斁灭如此。此时 君丧之礼。尤在宜厚而不宜薄也。前所上奉慰 小朝书。近因 大朝筵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6H 页
 中。叹无人劝讲 东宫。一大臣偶举贱臣有言。 上颇喜闻。仍 命索入书本。遂下 别谕。恩礼旷绝。至命递职而促召。其为皇陨愧汗。当复如何。当初此书。不过请勿过哀之意而已。虽有一二过去说话。而非直为言事之体者。今以是蒙被 异数至此。尤为踧踖。或者因此又有问此后语默当如何者。此则实不知前日之书。初非为言事而发。则今亦不可因此遂改其本来所守者也。不识高明将何以教之。 别谕后辄以一疏。敢悉暴情私。 圣批又甚恻怛。益令人感泣。不知死所。只此私义终无转动之路。将不免辜负 大恩。永为不瞑之鬼而已。奈何奈何。此事颠末。恐欲详知。玆录上。幸览还也。
中。叹无人劝讲 东宫。一大臣偶举贱臣有言。 上颇喜闻。仍 命索入书本。遂下 别谕。恩礼旷绝。至命递职而促召。其为皇陨愧汗。当复如何。当初此书。不过请勿过哀之意而已。虽有一二过去说话。而非直为言事之体者。今以是蒙被 异数至此。尤为踧踖。或者因此又有问此后语默当如何者。此则实不知前日之书。初非为言事而发。则今亦不可因此遂改其本来所守者也。不识高明将何以教之。 别谕后辄以一疏。敢悉暴情私。 圣批又甚恻怛。益令人感泣。不知死所。只此私义终无转动之路。将不免辜负 大恩。永为不瞑之鬼而已。奈何奈何。此事颠末。恐欲详知。玆录上。幸览还也。答宋晦可
祭祀行废。自有官者受衰以来。终觉栗翁说为有据。但未敢便为定论。俟更商量。时偕说。固亦昭陵之见。然曾子问注所论适子在家。自依时行亲丧之礼者。亦岂不严于君臣之礼而如是哉。恐或各有其义而非苟然耳。
答宋晦可
所谕昏礼。始亦非为一时事势。敢为无稽之言。如遂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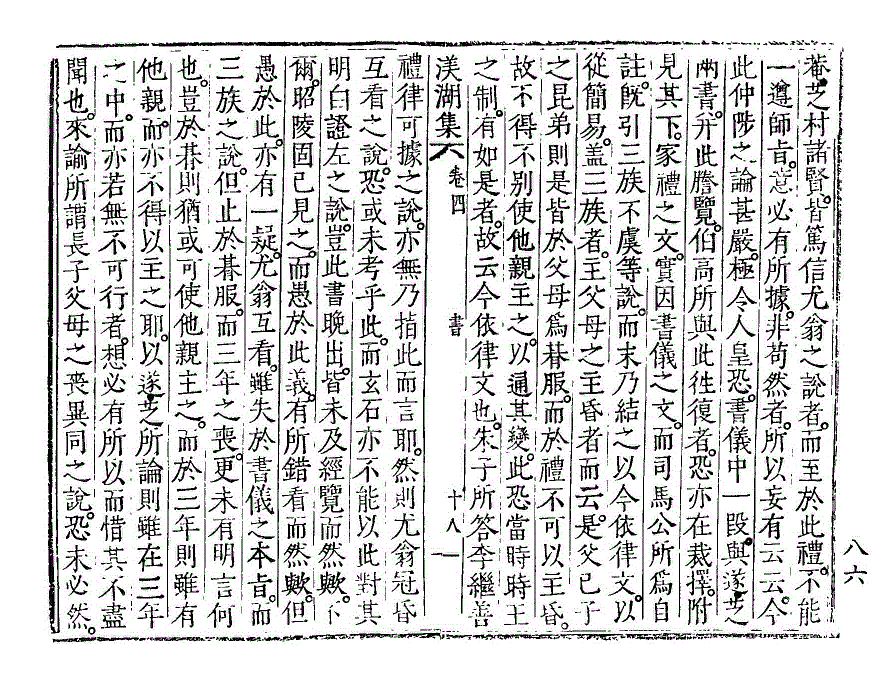 庵,芝村诸贤。皆笃信尤翁之说者。而至于此礼。不能一遵师旨。意必有所据。非苟然者。所以妄有云云。今此仲陟之论甚严。极令人皇恐。书仪中一段。与遂,芝两书。并此誊览。伯高所与此往复者。恐亦在裁择。附见其下。家礼之文。实因书仪之文。而司马公所为自注。既引三族不虞等说。而末乃结之以今依律文。以从简易。盖三族者。主父母之主昏者而云。是父己子之昆弟则是皆于父母为期服。而于礼不可以主昏。故不得不别使他亲主之。以通其变。此恐当时时王之制。有如是者。故云今依律文也。朱子所答李继善礼律可据之说。亦无乃指此而言耶。然则尤翁冠昏互看之说。恐或未考乎此。而玄石亦不能以此对其明白證左之说。岂此书晚出。皆未及经览而然欤。不尔。昭陵固已见之。而愚于此义。有所错看而然欤。但愚于此。亦有一疑。尤翁互看。虽失于书仪之本旨。而三族之说。但止于期服。而三年之丧。更未有明言何也。岂于期则犹或可使他亲主之。而于三年则虽有他亲。而亦不得以主之耶。以遂,芝所论则虽在三年之中。而亦若无不可行者。想必有所以而惜其不尽闻也。来谕所谓长子父母之丧异同之说。恐未必然。
庵,芝村诸贤。皆笃信尤翁之说者。而至于此礼。不能一遵师旨。意必有所据。非苟然者。所以妄有云云。今此仲陟之论甚严。极令人皇恐。书仪中一段。与遂,芝两书。并此誊览。伯高所与此往复者。恐亦在裁择。附见其下。家礼之文。实因书仪之文。而司马公所为自注。既引三族不虞等说。而末乃结之以今依律文。以从简易。盖三族者。主父母之主昏者而云。是父己子之昆弟则是皆于父母为期服。而于礼不可以主昏。故不得不别使他亲主之。以通其变。此恐当时时王之制。有如是者。故云今依律文也。朱子所答李继善礼律可据之说。亦无乃指此而言耶。然则尤翁冠昏互看之说。恐或未考乎此。而玄石亦不能以此对其明白證左之说。岂此书晚出。皆未及经览而然欤。不尔。昭陵固已见之。而愚于此义。有所错看而然欤。但愚于此。亦有一疑。尤翁互看。虽失于书仪之本旨。而三族之说。但止于期服。而三年之丧。更未有明言何也。岂于期则犹或可使他亲主之。而于三年则虽有他亲。而亦不得以主之耶。以遂,芝所论则虽在三年之中。而亦若无不可行者。想必有所以而惜其不尽闻也。来谕所谓长子父母之丧异同之说。恐未必然。渼湖集卷之四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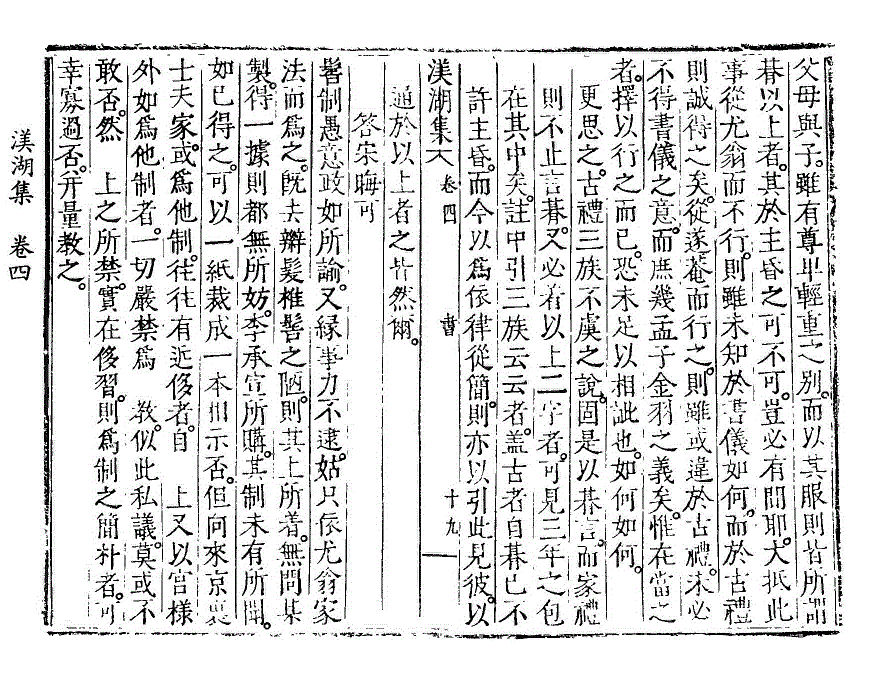 父母与子。虽有尊卑轻重之别。而以其服则皆所谓期以上者。其于主昏之可不可。岂必有间耶。大抵此事从尤翁而不行。则虽未知于书仪如何。而于古礼则诚得之矣。从遂庵而行之。则虽或违于古礼。未必不得书仪之意。而庶几孟子金羽之义矣。惟在当之者。择以行之而已。恐未足以相訾也。如何如何。
父母与子。虽有尊卑轻重之别。而以其服则皆所谓期以上者。其于主昏之可不可。岂必有间耶。大抵此事从尤翁而不行。则虽未知于书仪如何。而于古礼则诚得之矣。从遂庵而行之。则虽或违于古礼。未必不得书仪之意。而庶几孟子金羽之义矣。惟在当之者。择以行之而已。恐未足以相訾也。如何如何。更思之。古礼三族不虞之说。固是以期言。而家礼则不止言期。又必着以上二字者。可见三年之包在其中矣。注中引三族云云者。盖古者自期已不许主昏。而今以为依律从简。则亦以引此见彼。以通于以上者之皆然尔。
答宋晦可
髻制愚意政如所谕。又缘事力不逮。姑只依尤翁家法而为之。既去辫发椎髻之陋。则其上所着。无问某制。得一据则都无所妨。李承宣所购。其制未有所闻。如已得之。可以一纸裁成一本相示否。但向来京里士夫家。或为他制。往往有近侈者。自 上又以宫样外如为他制者。一切严禁为 教。似此私议。莫或不敢否。然 上之所禁。实在侈习。则为制之简朴者。可幸寡过否。并量教之。
答宋晦可
数日来。连有先声。方苦待贲临。书至。喜审雨水行驾利涉。起居增重。独恨不直抵此中。作一稳耳。今日之动。诚不获已者。而中外拭目。以观贤者所为。毁誉勿论。而惟尽吾义分。而无愧悔于此心为至难。不知所欲言者何事。亟欲进听一二。而闻将有史官之来。又似有宾客之挠。虽往恐未稳叙。终惜其舍此而他之耳。今夕如失临宿。则势须于归路逢迎。惟愿千万慎重。毋负士望。而卒为吾道之光也。不宣。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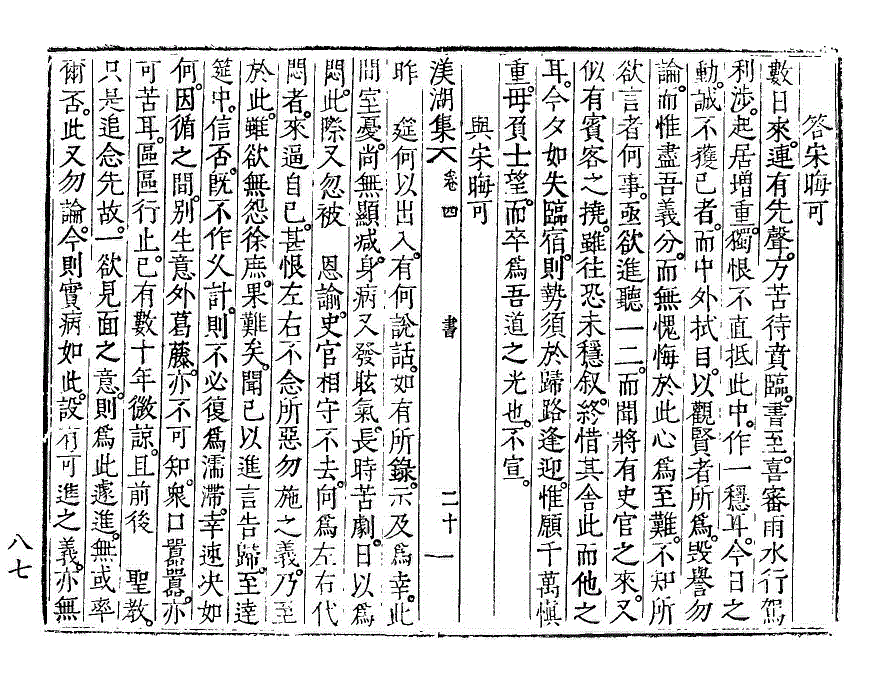 与宋晦可
与宋晦可昨 筵何以出入。有何说话。如有所录。示及为幸。此间室忧。尚无显减。身病又发眩气。长时苦剧。日以为闷。此际又忽被 恩谕。史官相守不去。向为左右代闷者。来逼自己。甚恨左右不念所恶勿施之义。乃至于此。虽欲无怨徐庶。果难矣。闻已以进言告归。至达筵中。信否。既不作久计。则不必复为濡滞。幸速决如何。因循之间。别生意外葛藤。亦不可知。众口嚣嚣。亦可苦耳。区区行止。已有数十年微谅。且前后 圣教。只是追念先故。一欲见面之意。则为此遽进。无或率尔否。此又勿论。今则实病如此。设有可进之义。亦无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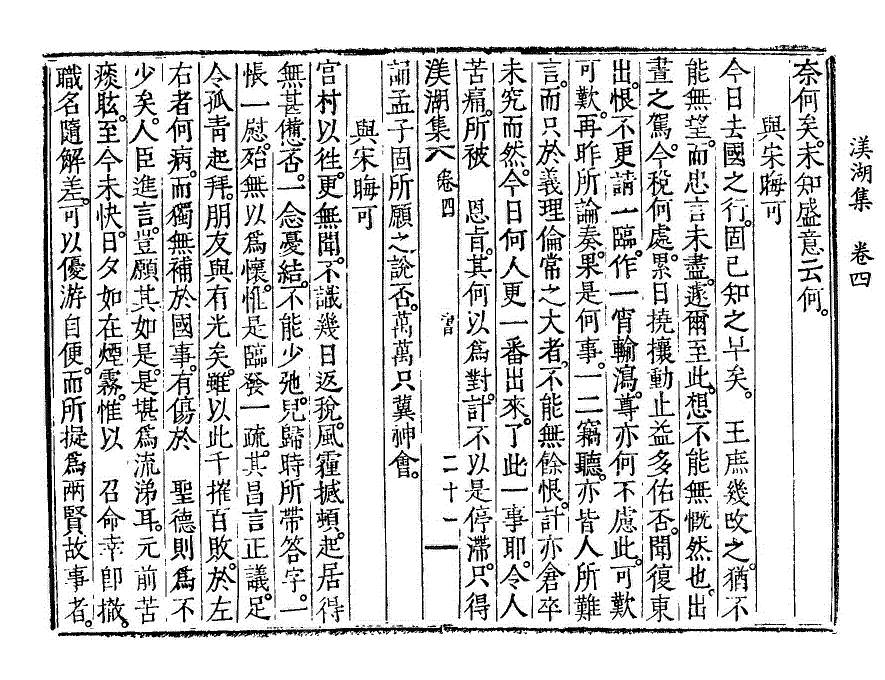 奈何矣。未知盛意云何。
奈何矣。未知盛意云何。与宋晦可
今日去国之行。固已知之早矣。 王庶几改之。犹不能无望。而忠言未尽。遽尔至此。想不能无慨然也。出昼之驾。今税何处。累日挠攘动止益多佑否。闻复东出。恨不更请一临。作一宵输泻。尊亦何不虑此。可叹可叹。再昨所论奏。果是何事。一二窃听。亦皆人所难言。而只于义理伦常之大者。不能无馀恨。计亦仓卒未究而然。今日何人更一番出来。了此一事耶。令人苦痛。所被 恩旨。其何以为对。计不以是停滞。只得诵孟子固所愿之说否。万万只冀神会。
与宋晦可
宫村以往。更无闻。不识几日返税。风霾撼顿。起居得无甚惫否。一念忧结。不能少弛。儿归时所带答字。一怅一慰。殆无以为怀。惟是临发一疏。其昌言正议。足令孤青起拜。朋友与有光矣。虽以此千摧百败。于左右者何病。而独无补于国事。有伤于 圣德则为不少矣。人臣进言。岂愿其如是。是堪为流涕耳。元前苦痰眩。至今未快。日夕如在烟雾。惟以 召命幸即撤。职名随解差。可以优游自便。而所拟为两贤故事者。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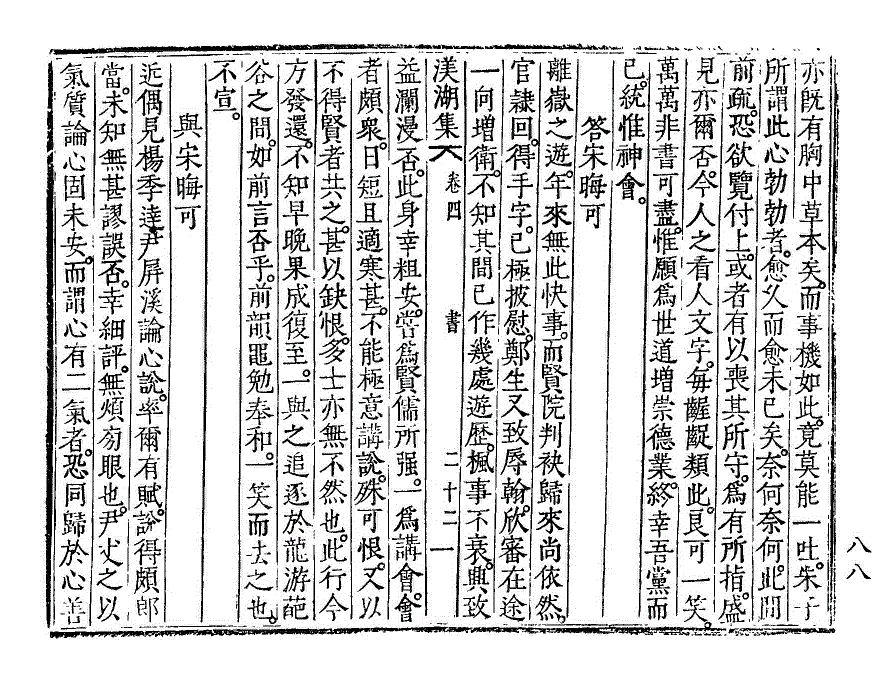 亦既有胸中草本矣。而事机如此。竟莫能一吐。朱子所谓此心勃勃者。愈久而愈未已矣。奈何奈何。此间前疏。恐欲览付上。或者有以丧其所守。为有所指。盛见亦尔否。今人之看人文字。每龌龊类此。良可一笑。万万非书可尽。惟愿为世道增崇德业。终幸吾党而已。统惟神会。
亦既有胸中草本矣。而事机如此。竟莫能一吐。朱子所谓此心勃勃者。愈久而愈未已矣。奈何奈何。此间前疏。恐欲览付上。或者有以丧其所守。为有所指。盛见亦尔否。今人之看人文字。每龌龊类此。良可一笑。万万非书可尽。惟愿为世道增崇德业。终幸吾党而已。统惟神会。答宋晦可
离岳之游。年来无此快事。而贤院判袂归来尚依然。官隶回。得手字。已极披慰。郑生又致辱翰。欣审在途一向增卫。不知其间已作几处游历。枫事不衰。兴致益澜漫否。此身幸粗安。尝为贤儒所强。一为讲会。会者颇众。日短且适寒甚。不能极意讲说。殊可恨。又以不得贤者共之。甚以缺恨。多士亦无不然也。此行今方发还。不知早晚果成复至。一与之追逐于龙游葩谷之间。如前言否乎。前韵黾勉奉和。一笑而去之也。不宣。
与宋晦可
近偶见杨季达,尹屏溪论心说。率尔有赋。说得颇郎当。未知无甚谬误否。幸细评。无烦旁眼也。尹丈之以气质论心固未安。而谓心有二气者。恐同归于心善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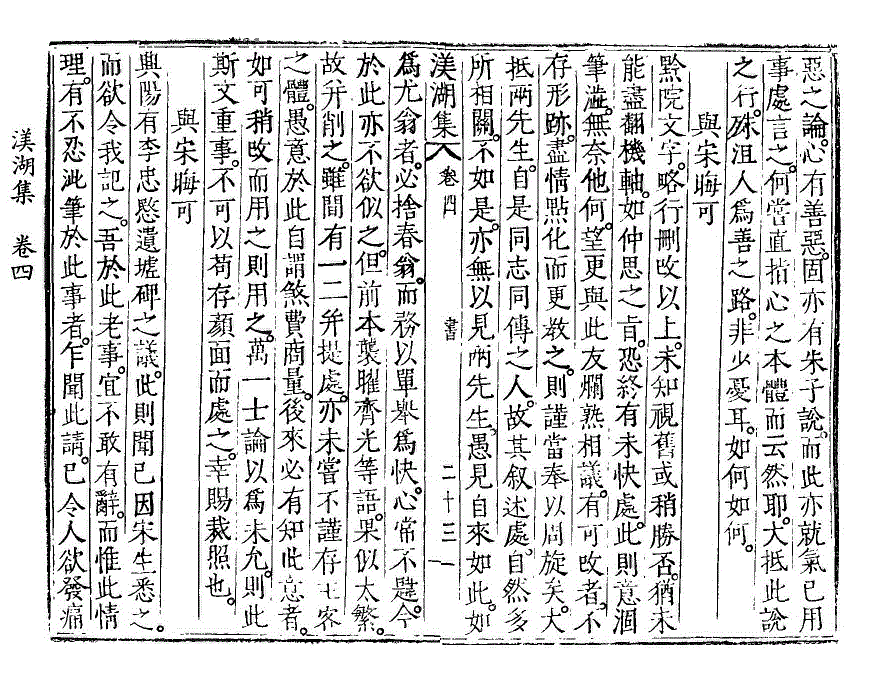 恶之论。心有善恶。固亦有朱子说。而此亦就气已用事处言之。何尝直指心之本体而云然耶。大抵此说之行。殊沮人为善之路。非少忧耳。如何如何。
恶之论。心有善恶。固亦有朱子说。而此亦就气已用事处言之。何尝直指心之本体而云然耶。大抵此说之行。殊沮人为善之路。非少忧耳。如何如何。与宋晦可
黔院文字。略行删改以上。未知视旧或稍胜否。犹未能尽翻机轴。如仲思之旨。恐终有未快处。此则意涸笔涩。无奈他何。望更与此友烂熟相议。有可改者。不存形迹。尽情点化而更教之。则谨当奉以周旋矣。大抵两先生。自是同志同传之人。故其叙述处。自然多所相关。不如是。亦无以见两先生。愚见自来如此。如为尤翁者。必舍春翁。而务以单举为快。心常不韪。今于此亦不欲似之。但前本袭曜齐光等语。果似太繁。故并削之。虽间有一二并提处。亦未尝不谨存主客之体。愚意于此自谓煞费商量。后来必有知此意者。如可稍改而用之则用之。万一士论以为未允。则此斯文重事。不可以苟存颜面而处之。幸赐裁照也。
与宋晦可
兴阳有李忠悯遗墟碑之议。此则闻已因宋生悉之。而欲令我记之。吾于此老事。宜不敢有辞。而惟此情理。有不忍泚笔于此事者。乍闻此请。已令人欲发痛
渼湖集卷之四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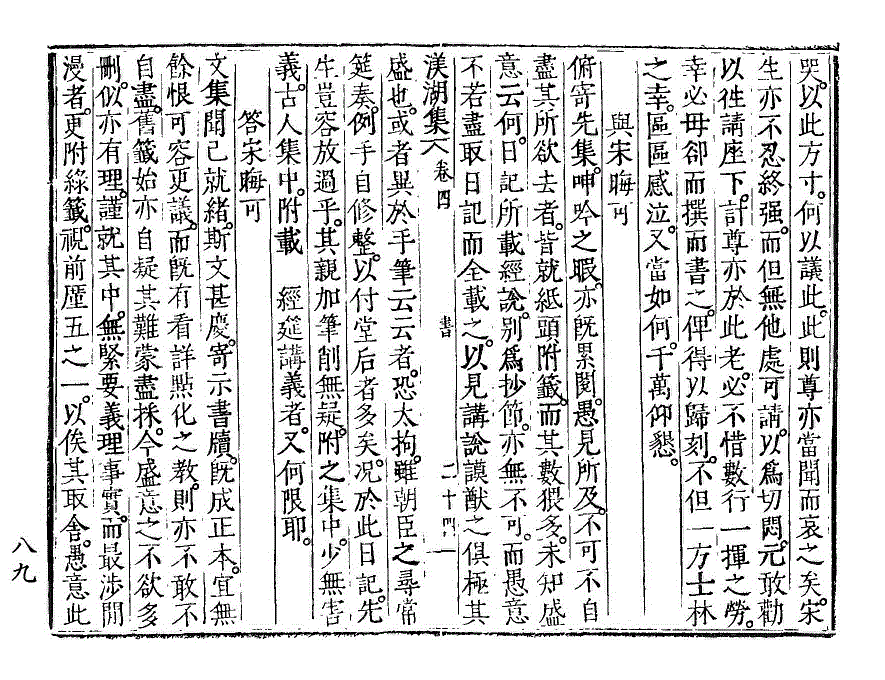 哭。以此方寸。何以议此。此则尊亦当闻而哀之矣。宋生亦不忍终强。而但无他处可请。以为切闷。元敢劝以往请座下。计尊亦于此老。必不惜数行一挥之劳。幸必毋却而撰而书之。俾得以归刻。不但一方士林之幸。区区感泣。又当如何。千万仰恳。
哭。以此方寸。何以议此。此则尊亦当闻而哀之矣。宋生亦不忍终强。而但无他处可请。以为切闷。元敢劝以往请座下。计尊亦于此老。必不惜数行一挥之劳。幸必毋却而撰而书之。俾得以归刻。不但一方士林之幸。区区感泣。又当如何。千万仰恳。与宋晦可
俯寄先集。呻吟之暇。亦既累阅。愚见所及。不可不自尽其所欲去者。皆就纸头附签。而其数猥多。未知盛意云何。日记所载经说。别为抄节。亦无不可。而愚意不若尽取日记而全载之。以见讲说谟猷之俱极其盛也。或者异于手笔云云者。恐太拘。虽朝臣之寻常筵奏。例手自修整。以付堂后者多矣。况于此日记。先生岂容放过乎。其亲加笔削无疑。附之集中。少无害义。古人集中。附载 经筵讲义者。又何限耶。
答宋晦可
文集闻已就绪。斯文甚庆。寄示书牍。既成正本。宜无馀恨可容更议。而既有看详点化之教。则亦不敢不自尽。旧签始亦自疑其难蒙尽采。今盛意之不欲多删。似亦有理。谨就其中。无紧要义理事实。而最涉閒漫者。更附绿签。视前廑五之一。以俟其取舍。愚意此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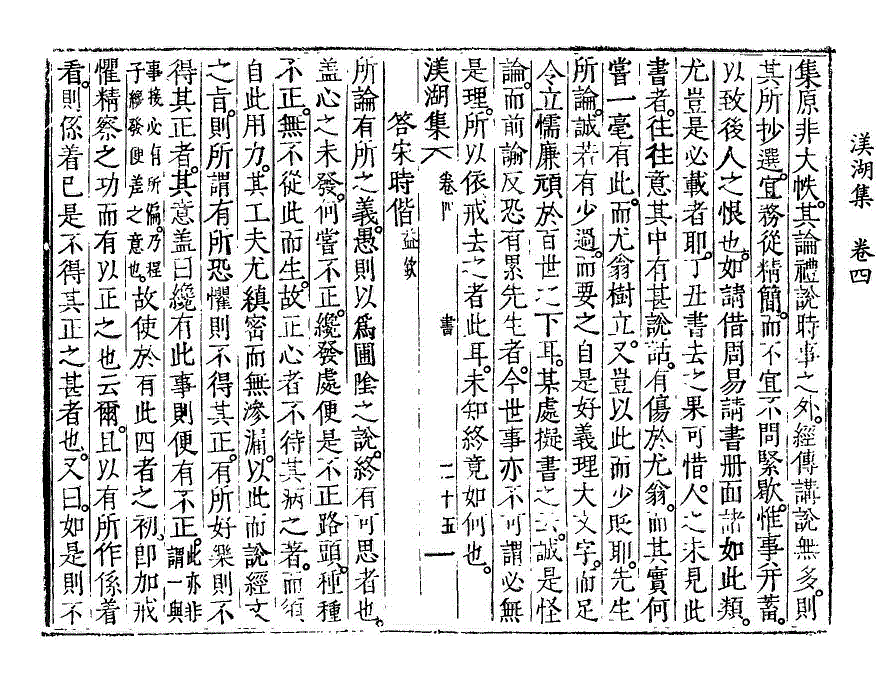 集原非大帙。其论礼说时事之外。经传讲说无多。则其所抄选。宜务从精简。而不宜不问紧歇。惟事并蓄。以致后人之恨也。如请借周易请书册面诸如此类。尤岂是必载者耶。丁丑书去之果可惜。人之未见此书者。往往意其中有甚说话。有伤于尤翁。而其实何尝一毫有此。而尤翁树立。又岂以此而少贬耶。先生所论。诚若有少过。而要之自是好义理大文字。而足令立懦廉顽于百世之下耳。某处拟书之云。诚是怪论。而前谕反恐有累先生者。今世事亦不可谓必无是理。所以依戒去之者此耳。未知终竟如何也。
集原非大帙。其论礼说时事之外。经传讲说无多。则其所抄选。宜务从精简。而不宜不问紧歇。惟事并蓄。以致后人之恨也。如请借周易请书册面诸如此类。尤岂是必载者耶。丁丑书去之果可惜。人之未见此书者。往往意其中有甚说话。有伤于尤翁。而其实何尝一毫有此。而尤翁树立。又岂以此而少贬耶。先生所论。诚若有少过。而要之自是好义理大文字。而足令立懦廉顽于百世之下耳。某处拟书之云。诚是怪论。而前谕反恐有累先生者。今世事亦不可谓必无是理。所以依戒去之者此耳。未知终竟如何也。答宋时偕(益钦)
所论有所之义。愚则以为圃阴之说。终有可思者也。盖心之未发。何尝不正。才发处便是不正路头。种种不正。无不从此而生。故正心者不待其病之著。而须自此用力。其工夫尤缜密而无渗漏。以此而说经文之旨。则所谓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者。其意盖曰才有此事则便有不正。(此亦非谓一与事接必有所偏。乃程子才发便差之意也。)故使于有此四者之初。即加戒惧精察之功而有以正之也云尔。且以有所作系着看。则系着已是不得其正之甚者也。又曰。如是则不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0L 页
 得其正者。无乃冗乎。虽然。自朱子以来。作系着说者。亦非一矣。愚何敢自信也。
得其正者。无乃冗乎。虽然。自朱子以来。作系着说者。亦非一矣。愚何敢自信也。答李仪韶
乾之九二文言。只曰正中。而不曰中正。盖言其不潜未跃。正当中之时也。不谓其以阳居阴。亦得其正也。然传义诸说。皆以中正言之者何耶。
所谕正中言其不潜未跃。正当中之时者得之。如传所谓在卦之正中。本义所谓正中不潜而未跃之时。皆是如此。今言传义诸说。皆以中正言之者。何也。
震之六二亿丧贝之亿字。未有明释。而按此卦六五爻辞曰亿无丧。而夫子释之曰大无丧也。以此例之。则恐亦为大丧货贝之义。未知如何。
旧读此。每亦疑其如此。字书又曰亿大也。
三渊先生诗曰。未曾看系辞。知易为何物。烂诵却回看。群龙毛色别。此言与程朱所示门径。大段差别。想必有所以然者。愿闻之。
渊祖说。固与程朱所指不同。然各有一义。何也。盖系辞者。本所以明易。故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此所以有不看卦爻而看系辞。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序例之说。此固两先生之意也。然其理数法象之森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1H 页
 然者。固亦莫不各具于六十四卦之中。而学者未必能尽察也。及孔子又明白发挥于系辞之文。然后所谓群龙之毛色者。种种呈露。殆无遗蕴。而易之为物。始益灿然而可睹矣。此又渊祖所说之指欤。如此看。不知如何。
然者。固亦莫不各具于六十四卦之中。而学者未必能尽察也。及孔子又明白发挥于系辞之文。然后所谓群龙之毛色者。种种呈露。殆无遗蕴。而易之为物。始益灿然而可睹矣。此又渊祖所说之指欤。如此看。不知如何。答李仪韶
冠礼非如繁华设乐之仪。虽在 国恤中。因山既过。则似无不可行之义。盖昏重于冠。而嫁娶尚且许之。况其轻者乎。虽曰方丧重于私期。私期中。礼不得主昏。而持方丧者。无不得主昏之文。是方丧有时而不如私期者。可见矣。但宾主服色。则有官者用白帽白带。无官则用白笠白带。近日京里诸家。多如是行之。恐为得宜。而至如醴宾酒馔。宜亦稍从简约。以示变焉耳。
与李仪韶
春暮一书。至今披慰。而贱疾沉绵数月。殆废人事。讫未有谢语。想深讶也。天时正热。閒中起居冲适。玩索益有趣否。向因伯讷。得见太极西铭数说。皆甚好。此外亦须有多少记述。恨无以尽得而一读之也。如以一二因便垂示则幸也。蒙谕出处之义。所以牖迷者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1L 页
 甚悉。令人感叹。区区不肖于两祖。皆无能为役。然默观今日。虽使古人之学识通明力量过人者当之。将无所措其手。其馀又可论耶。为今私计。不若退守本分。犹可以寡过。而乃其情则非敢出于苟洁身名。如来书之云也。向尝以一疏。悉暴悲苦之私。而疏上三月。犹未蒙上彻。进退皆不暇言。而日夜惶惧。惟俟鈇钺之加而已。先集一卷。蒙此委示。良荷不鄙。别纸申谕。读来不觉涕下。序文之托。诚不敢当。亦何忍以不文而终辞也。但年来病甚衰剧。恐难以时日为期。幸宽俟之。亦非敢有故为延拖之意也。
甚悉。令人感叹。区区不肖于两祖。皆无能为役。然默观今日。虽使古人之学识通明力量过人者当之。将无所措其手。其馀又可论耶。为今私计。不若退守本分。犹可以寡过。而乃其情则非敢出于苟洁身名。如来书之云也。向尝以一疏。悉暴悲苦之私。而疏上三月。犹未蒙上彻。进退皆不暇言。而日夜惶惧。惟俟鈇钺之加而已。先集一卷。蒙此委示。良荷不鄙。别纸申谕。读来不觉涕下。序文之托。诚不敢当。亦何忍以不文而终辞也。但年来病甚衰剧。恐难以时日为期。幸宽俟之。亦非敢有故为延拖之意也。与洪养之
此间廑廑支吾。积水四环。人客罕至。朝夕只取一部朱子大全。随意看读。不无意趣。其间亦多抚卷欣慨处。但傍无师友与之上下讨论。每想吾兄。为之怅然也。抑区区每愿窃有献焉。夫以吾兄天质之粹。学识之精。苟于此事。少加之意。将何远之不可到。而惜乎其不免于科宦之累。虚送过去岁月。而今不幸至于大故。古人亦于此得有以感奋自力。以进其德者多矣。盖当哀苦澹泊之中。外诱自少。善端易著。其理然也。兄于此事。今日所占。亦可谓自有六七分。所少者。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2H 页
 但卓然必学圣人之志耳。苟能先立此志。而更取旧读之书而玩绎焉。于朱子所谓居敬穷理力行三者。专心一意。日有孜孜。而勿以苟且流循之意参焉。其进也孰御焉。迩来欲以此一闻久矣。而病骸当此潦炎。日夕㱡㱡。含意未遂。今始因笔及之。未知盛意云何。
但卓然必学圣人之志耳。苟能先立此志。而更取旧读之书而玩绎焉。于朱子所谓居敬穷理力行三者。专心一意。日有孜孜。而勿以苟且流循之意参焉。其进也孰御焉。迩来欲以此一闻久矣。而病骸当此潦炎。日夕㱡㱡。含意未遂。今始因笔及之。未知盛意云何。与洪养之
此行发程翌日。无事抵松都。留憩两日。来早将寻朴渊诸胜。自此遂转而益西。仙楼失贤主人。为可叹惜。然路上相见谓已留济胜之资。而复以伊天为其兼官。亦不至太落莫矣。昨日暂上满月台。已令人不胜废兴之感。转拜崧阳庙。仍寻善竹桥。观所谓血痕处。又为之流涕。令伴游者。唱先生遗词数阕。听者无不歔欷欲绝。忠义之动人如是耶。
答洪养之
别怀与秋俱深。忽承今月初一惠书。获审霜寒行中起居神劳增福。区区欣慰。何可以笔舌既也。信后又复多日。计程想已抵营久矣。游至此亦壮矣。其览观山川。歌咏谣俗。想已富有之矣。可因风寄其一二否。但一路凶荒如彼。没兴又可知。归事因此渐迟。则殊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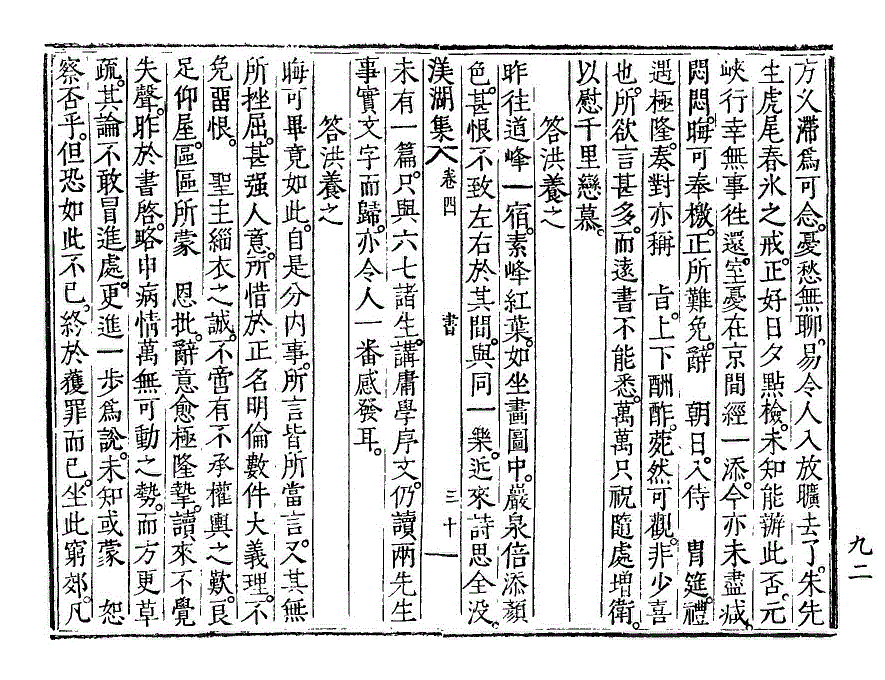 方久滞为可念。忧愁无聊。易令人入放旷去了。朱先生虎尾春冰之戒。正好日夕点检。未知能办此否。元峡行幸无事往还。室忧在京间经一添。今亦未尽减。闷闷。晦可奉檄。正所难免。辞 朝日。入侍 胄筵。礼遇极隆。奏对亦称 旨。上下酬酢。菀然可观。非少喜也。所欲言甚多。而远书不能悉。万万只祝随处增卫。以慰千里恋慕。
方久滞为可念。忧愁无聊。易令人入放旷去了。朱先生虎尾春冰之戒。正好日夕点检。未知能办此否。元峡行幸无事往还。室忧在京间经一添。今亦未尽减。闷闷。晦可奉檄。正所难免。辞 朝日。入侍 胄筵。礼遇极隆。奏对亦称 旨。上下酬酢。菀然可观。非少喜也。所欲言甚多。而远书不能悉。万万只祝随处增卫。以慰千里恋慕。答洪养之
昨往道峰一宿。素峰红叶。如坐画图中。岩泉倍添颜色。甚恨不致左右于其间。与同一乐。近来诗思全没。未有一篇。只与六七诸生。讲庸学序文。仍读两先生事实文字而归。亦令人一番感发耳。
答洪养之
晦可毕竟如此。自是分内事。所言皆所当言。又其无所挫屈。甚强人意。所惜于正名明伦数件大义理。不免留恨。 圣主缁衣之诚。不啻有不承权舆之叹。良足仰屋。区区所蒙 恩批。辞意愈极隆挚。读来不觉失声。昨于书启。略申病情万无可动之势。而方更草疏。其论不敢冒进处。更进一步为说。未知或蒙 恕察否乎。但恐如此不已。终于获罪而已。坐此穷郊。凡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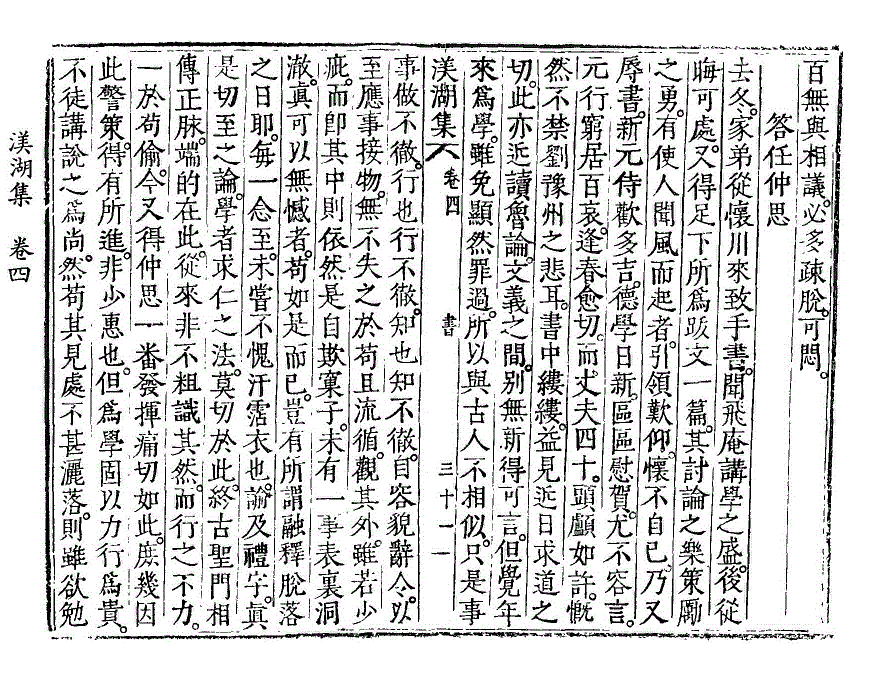 百无与相议。必多疏脱。可闷。
百无与相议。必多疏脱。可闷。答任仲思
去冬。家弟从怀川来致手书。闻飞庵讲学之盛。后从晦可处。又得足下所为跋文一篇。其讨论之乐策励之勇。有使人闻风而起者。引领叹仰。怀不自已。乃又辱书。新元侍欢多吉。德学日新。区区慰贺。尤不容言。元行穷居百哀。逢春愈切。而丈夫四十。头颅如许。慨然不禁刘豫州之悲耳。书中缕缕。益见近日求道之切。此亦近读鲁论。文义之间。别无新得可言。但觉年来为学。虽免显然罪过。所以与古人不相似。只是事事做不彻。行也行不彻。知也知不彻。自容貌辞令。以至应事接物。无不失之于苟且流循。观其外。虽若少疵。而即其中则依然是自欺窠子。未有一事表里洞澈。真可以无憾者。苟如是而已。岂有所谓融释脱落之日耶。每一念至。未尝不愧汗沾衣也。谕及礼字。真是切至之论。学者求仁之法。莫切于此。终古圣门相传正脉。端的在此。从来非不粗识其然。而行之不力。一于苟偷。今又得仲思一番发挥痛切如此。庶几因此警策。得有所进。非少惠也。但为学固以力行为贵。不徒讲说之为尚。然苟其见处不甚洒落。则虽欲勉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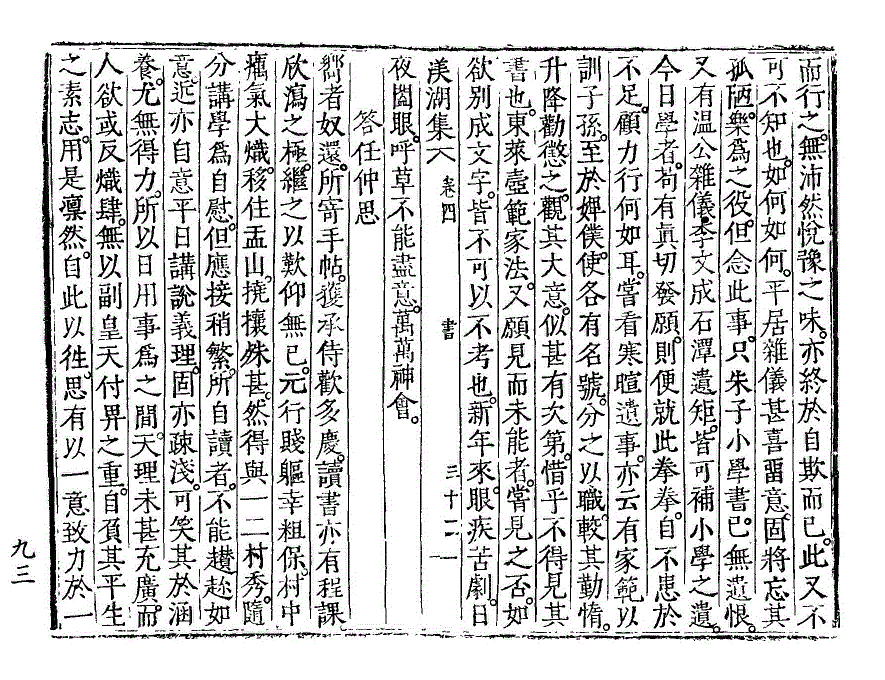 而行之。无沛然悦豫之味。亦终于自欺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如何如何。平居杂仪甚喜留意。固将忘其孤陋。乐为之役。但念此事。只朱子小学书。已无遗恨。又有温公杂仪,李文成石潭遗矩。皆可补小学之遗。今日学者。苟有真切发愿。则便就此拳拳。自不患于不足。顾力行何如耳。尝看寒暄遗事。亦云有家范以训子孙。至于婢仆。使各有名号。分之以职。较其勤惰。升降劝惩之。观其大意。似甚有次第。惜乎不得见其书也。东莱壸范家法。又愿见而未能者。尝见之否。如欲别成文字。皆不可以不考也。新年来。眼疾苦剧。日夜阖眼。呼草不能尽意。万万神会。
而行之。无沛然悦豫之味。亦终于自欺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如何如何。平居杂仪甚喜留意。固将忘其孤陋。乐为之役。但念此事。只朱子小学书。已无遗恨。又有温公杂仪,李文成石潭遗矩。皆可补小学之遗。今日学者。苟有真切发愿。则便就此拳拳。自不患于不足。顾力行何如耳。尝看寒暄遗事。亦云有家范以训子孙。至于婢仆。使各有名号。分之以职。较其勤惰。升降劝惩之。观其大意。似甚有次第。惜乎不得见其书也。东莱壸范家法。又愿见而未能者。尝见之否。如欲别成文字。皆不可以不考也。新年来。眼疾苦剧。日夜阖眼。呼草不能尽意。万万神会。答任仲思
向者奴还。所寄手帖。获承侍欢多庆。读书亦有程课。欣泻之极。继之以叹仰无已。元行贱躯幸粗保。村中疠气大炽。移住盂山。挠攘殊甚。然得与一二村秀。随分讲学为自慰。但应接稍繁。所自读者。不能趱趁如意。近亦自意平日讲说义理。固亦疏浅。可笑其于涵养。尤无得力。所以日用事为之间。天理未甚充广。而人欲或反炽肆。无以副皇天付畀之重。自负其平生之素志。用是凛然。自此以往。思有以一意致力于一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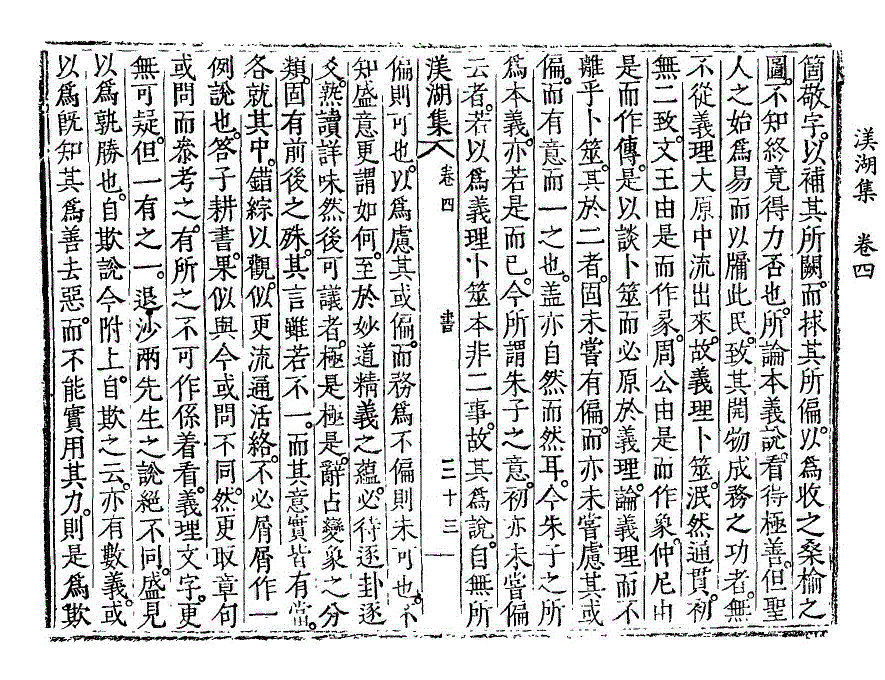 个敬字。以补其所阙。而救其所偏。以为收之桑榆之图。不知终竟得力否也。所论本义说。看得极善。但圣人之始为易而以牖此民。致其开物成务之功者。无不从义理大原中流出来。故义理卜筮。泯然通贯。初无二致。文王由是而作彖。周公由是而作象。仲尼由是而作传。是以谈卜筮而必原于义理。论义理而不离乎卜筮。其于二者。固未尝有偏。而亦未尝虑其或偏。而有意而一之也。盖亦自然而然耳。今朱子之所为本义。亦若是而已。今所谓朱子之意。初亦未尝偏云者。若以为义理卜筮本非二事。故其为说。自无所偏则可也。以为虑其或偏。而务为不偏则未可也。不知盛意更谓如何。至于妙道精义之蕴。必待逐卦逐爻。熟读详味然后可议者。极是极是。辞占变象之分类。固有前后之殊。其言虽若不一。而其意实皆有当。各就其中。错综以观。似更流通活络。不必屑屑作一例说也。答子耕书。果似与今或问不同。然更取章句或问而参考之。有所之不可作系着看。义理文字。更无可疑。但一有之一。退,沙两先生之说绝不同。盛见以为孰胜也。自欺说今附上。自欺之云。亦有数义。或以为既知其为善去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则是为欺
个敬字。以补其所阙。而救其所偏。以为收之桑榆之图。不知终竟得力否也。所论本义说。看得极善。但圣人之始为易而以牖此民。致其开物成务之功者。无不从义理大原中流出来。故义理卜筮。泯然通贯。初无二致。文王由是而作彖。周公由是而作象。仲尼由是而作传。是以谈卜筮而必原于义理。论义理而不离乎卜筮。其于二者。固未尝有偏。而亦未尝虑其或偏。而有意而一之也。盖亦自然而然耳。今朱子之所为本义。亦若是而已。今所谓朱子之意。初亦未尝偏云者。若以为义理卜筮本非二事。故其为说。自无所偏则可也。以为虑其或偏。而务为不偏则未可也。不知盛意更谓如何。至于妙道精义之蕴。必待逐卦逐爻。熟读详味然后可议者。极是极是。辞占变象之分类。固有前后之殊。其言虽若不一。而其意实皆有当。各就其中。错综以观。似更流通活络。不必屑屑作一例说也。答子耕书。果似与今或问不同。然更取章句或问而参考之。有所之不可作系着看。义理文字。更无可疑。但一有之一。退,沙两先生之说绝不同。盛见以为孰胜也。自欺说今附上。自欺之云。亦有数义。或以为既知其为善去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则是为欺渼湖集卷之四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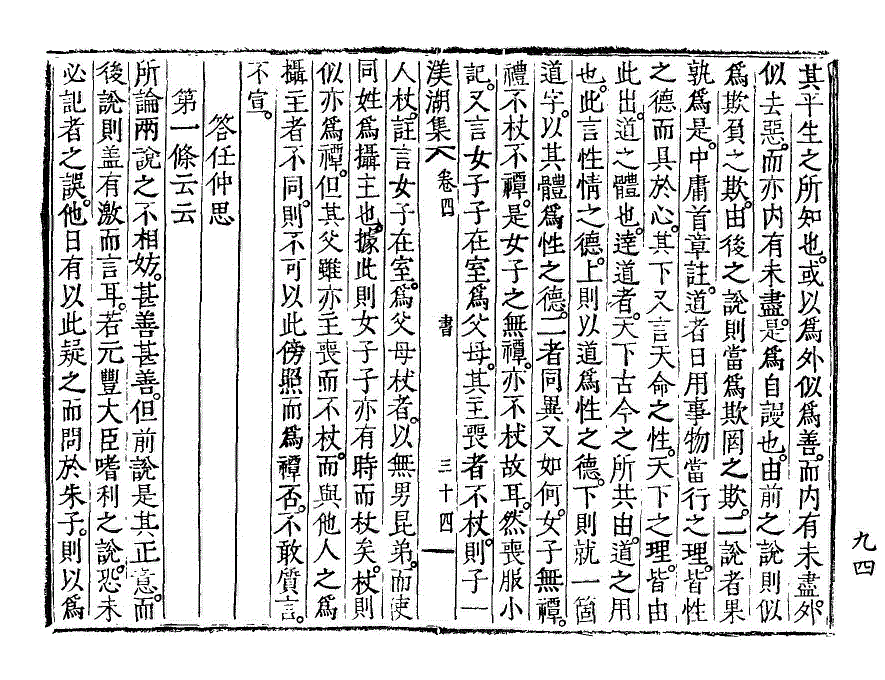 其平生之所知也。或以为外似为善。而内有未尽。外似去恶。而亦内有未尽。是为自谩也。由前之说则似为欺负之欺。由后之说则当为欺罔之欺。二说者果孰为是。中庸首章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其下又言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上则以道为性之德。下则就一个道字。以其体为性之德。二者同异又如何。女子无禫。礼不杖不禫。是女子之无禫。亦不杖故耳。然丧服小记。又言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注言女子在室。为父母杖者。以无男昆弟。而使同姓为摄主也。据此则女子子亦有时而杖矣。杖则似亦为禫。但其父虽亦主丧而不杖。而与他人之为摄主者不同。则不可以此傍照而为禫否。不敢质言。不宣。
其平生之所知也。或以为外似为善。而内有未尽。外似去恶。而亦内有未尽。是为自谩也。由前之说则似为欺负之欺。由后之说则当为欺罔之欺。二说者果孰为是。中庸首章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其下又言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上则以道为性之德。下则就一个道字。以其体为性之德。二者同异又如何。女子无禫。礼不杖不禫。是女子之无禫。亦不杖故耳。然丧服小记。又言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注言女子在室。为父母杖者。以无男昆弟。而使同姓为摄主也。据此则女子子亦有时而杖矣。杖则似亦为禫。但其父虽亦主丧而不杖。而与他人之为摄主者不同。则不可以此傍照而为禫否。不敢质言。不宣。答任仲思
第一条云云
所论两说之不相妨。甚善甚善。但前说是其正意。而后说则盖有激而言耳。若元丰大臣嗜利之说。恐未必记者之误。他日有以此疑之而问于朱子。则以为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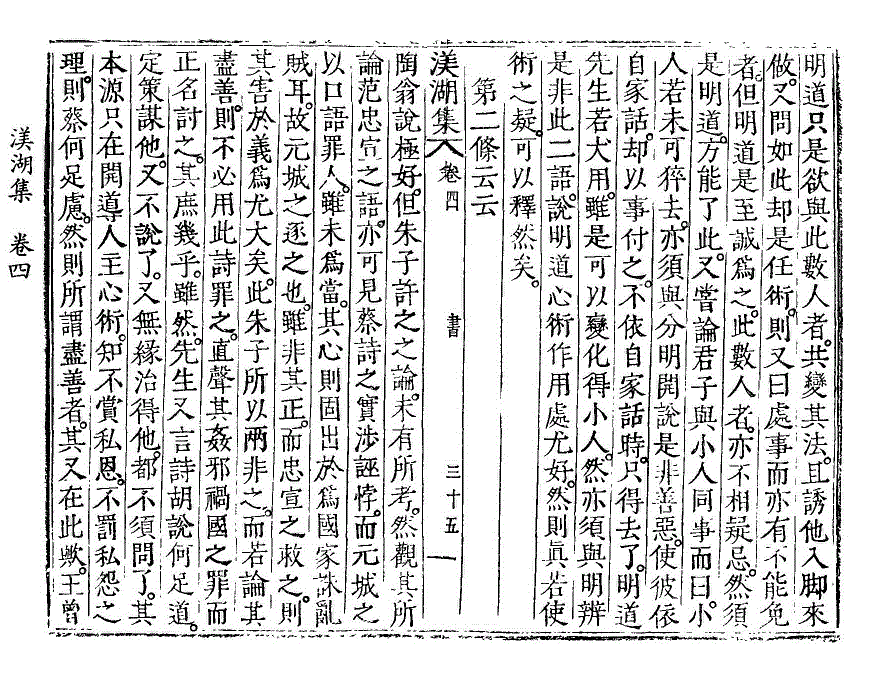 明道只是欲与此数人者。共变其法。且诱他入脚来做。又问如此却是任术。则又曰处事而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诚为之。此数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须是明道。方能了此。又尝论君子与小人同事而曰。小人若未可猝去。亦须与分明开说是非善恶。使彼依自家话。却以事付之。不依自家话时。只得去了。明道先生若犬用。虽是可以变化得小人。然亦须与明辨是非此二语。说明道心术作用处尤好。然则真若使术之疑。可以释然矣。
明道只是欲与此数人者。共变其法。且诱他入脚来做。又问如此却是任术。则又曰处事而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诚为之。此数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须是明道。方能了此。又尝论君子与小人同事而曰。小人若未可猝去。亦须与分明开说是非善恶。使彼依自家话。却以事付之。不依自家话时。只得去了。明道先生若犬用。虽是可以变化得小人。然亦须与明辨是非此二语。说明道心术作用处尤好。然则真若使术之疑。可以释然矣。第二条云云
陶翁说极好。但朱子许之之论。未有所考。然观其所论范忠宣之语。亦可见蔡诗之实涉诬悖。而元城之以口语罪人。虽未为当。其心则固出于为国家诛乱贼耳。故元城之逐之也。虽非其正。而忠宣之救之。则其害于义为尤大矣。此朱子所以两非之。而若论其尽善。则不必用此诗罪之。直声其奸邪祸国之罪而正名讨之。其庶几乎。虽然。先生又言诗胡说何足道。定策谋他。又不说了。又无缘治得他。都不须问了。其本源只在开导人主心术。知不赏私恩。不罚私怨之理。则蔡何足虑。然则所谓尽善者。其又在此欤。王曾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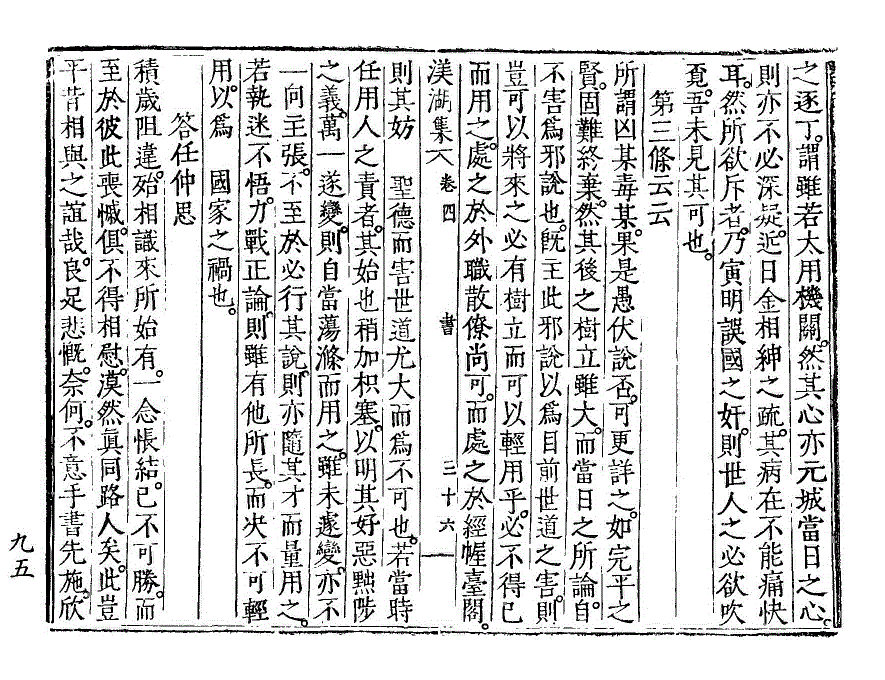 之逐丁。谓虽若太用机关。然其心亦元城当日之心。则亦不必深疑。近日金相绅之疏。其病在不能痛快耳。然所欲斥者。乃寅明误国之奸。则世人之必欲吹觅。吾未见其可也。
之逐丁。谓虽若太用机关。然其心亦元城当日之心。则亦不必深疑。近日金相绅之疏。其病在不能痛快耳。然所欲斥者。乃寅明误国之奸。则世人之必欲吹觅。吾未见其可也。第三条云云
所谓凶某毒某。果是愚伏说否。可更详之。如完平之贤。固难终弃。然其后之树立虽大。而当日之所论。自不害为邪说也。既主此邪说以为目前世道之害。则岂可以将来之必有树立而可以轻用乎。必不得已而用之。处之于外职散僚尚可。而处之于经幄台阁。则其妨 圣德而害世道尤大而为不可也。若当时任用人之责者。其始也稍加枳塞。以明其好恶黜陟之义。万一遂变。则自当荡涤而用之。虽未遽变。亦不一向主张。不至于必行其说。则亦随其才而量用之。若执迷不悟。力战正论。则虽有他所长。而决不可轻用。以为 国家之祸也。
答任仲思
积岁阻违。殆相识来所始有。一念怅结。已不可胜。而至于彼此丧戚。俱不得相慰。漠然真同路人矣。此岂平昔相与之谊哉。良足悲慨。奈何。不意手书先施。欣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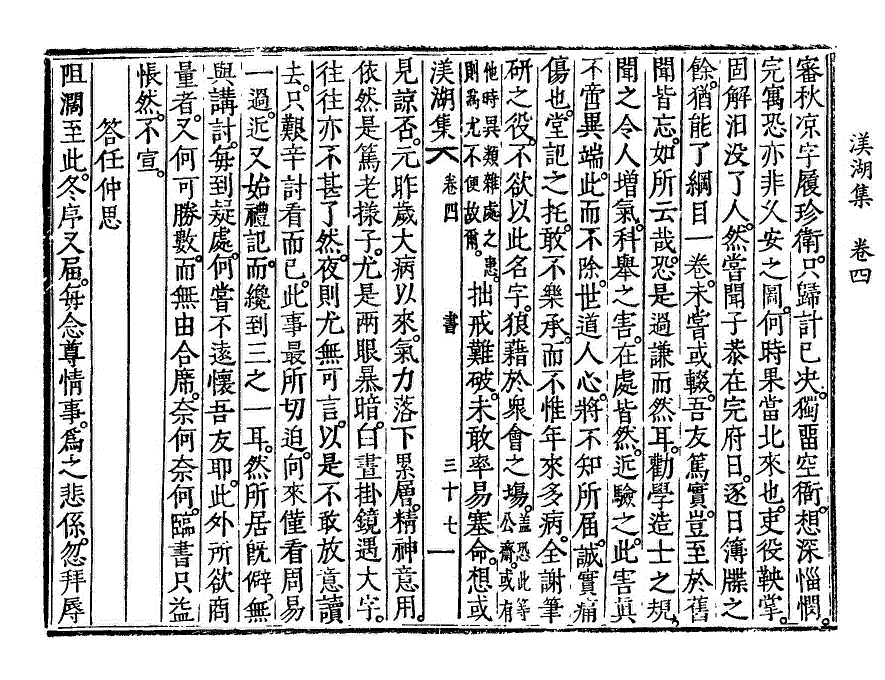 审秋凉字履珍卫。只归计已决。独留空衙。想深恼悯。完寓恐亦非久安之图。何时果当北来也。吏役鞅掌。固解汨没了人。然尝闻子恭在完府日。逐日簿牒之馀。犹能了纲目一卷。未尝或辍。吾友笃实。岂至于旧闻皆忘。如所云哉。恐是过谦而然耳。劝学造士之规。闻之令人增气。科举之害。在处皆然。近验之。此害真不啻异端。此而不除。世道人心。将不知所届。诚实痛伤也。堂记之托。敢不乐承。而不惟年来多病。全谢笔研之役。不欲以此名字。狼藉于众会之场。(盖恐此等公斋。或有他时异类杂处之患。则为尤不便故尔。)拙戒难破。未敢率易塞命。想或见谅否。元昨岁大病以来。气力落下累层。精神意用。依然是笃老㨾子。尤是两眼暴暗。白昼挂镜遇大字。往往亦不甚了然。夜则尤无可言。以是不敢放意读去。只艰辛讨看而已。此事最所切迫。向来仅看周易一过。近又始礼记。而才到三之一耳。然所居既僻。无与讲讨。每到疑处。何尝不远怀吾友耶。此外所欲商量者。又何可胜数。而无由合席。奈何奈何。临书只益怅然。不宣。
审秋凉字履珍卫。只归计已决。独留空衙。想深恼悯。完寓恐亦非久安之图。何时果当北来也。吏役鞅掌。固解汨没了人。然尝闻子恭在完府日。逐日簿牒之馀。犹能了纲目一卷。未尝或辍。吾友笃实。岂至于旧闻皆忘。如所云哉。恐是过谦而然耳。劝学造士之规。闻之令人增气。科举之害。在处皆然。近验之。此害真不啻异端。此而不除。世道人心。将不知所届。诚实痛伤也。堂记之托。敢不乐承。而不惟年来多病。全谢笔研之役。不欲以此名字。狼藉于众会之场。(盖恐此等公斋。或有他时异类杂处之患。则为尤不便故尔。)拙戒难破。未敢率易塞命。想或见谅否。元昨岁大病以来。气力落下累层。精神意用。依然是笃老㨾子。尤是两眼暴暗。白昼挂镜遇大字。往往亦不甚了然。夜则尤无可言。以是不敢放意读去。只艰辛讨看而已。此事最所切迫。向来仅看周易一过。近又始礼记。而才到三之一耳。然所居既僻。无与讲讨。每到疑处。何尝不远怀吾友耶。此外所欲商量者。又何可胜数。而无由合席。奈何奈何。临书只益怅然。不宣。答任仲思
阻阔至此。冬序又届。每念尊情事。为之悲系。忽拜辱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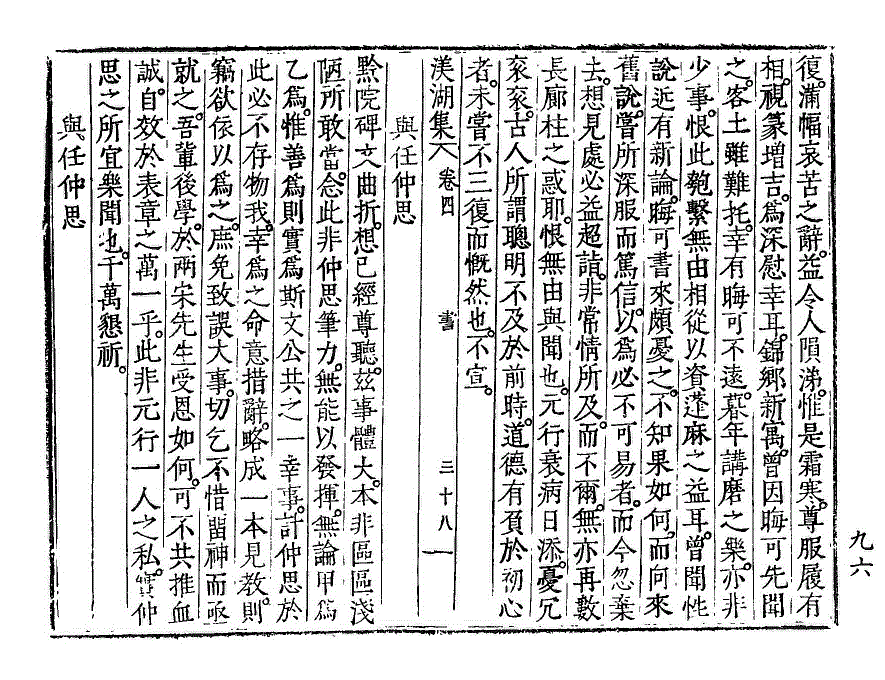 复。满幅哀苦之辞。益令人陨涕。惟是霜寒。尊服履有相。视篆增吉。为深慰幸耳。锦乡新寓。曾因晦可先闻之。客土虽难托。幸有晦可不远。暮年讲磨之乐。亦非少事。恨此匏系无由相从以资蓬麻之益耳。曾闻性说近有新论。晦可书来颇忧之。不知果如何。而向来旧说。尝所深服而笃信。以为必不可易者。而今忽弃去。想见处必益超诣。非常情所及。而不尔。无亦再数长廊柱之惑耶。恨无由与闻也。元行衰病日添。忧冗衮衮。古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者。未尝不三复而慨然也。不宣。
复。满幅哀苦之辞。益令人陨涕。惟是霜寒。尊服履有相。视篆增吉。为深慰幸耳。锦乡新寓。曾因晦可先闻之。客土虽难托。幸有晦可不远。暮年讲磨之乐。亦非少事。恨此匏系无由相从以资蓬麻之益耳。曾闻性说近有新论。晦可书来颇忧之。不知果如何。而向来旧说。尝所深服而笃信。以为必不可易者。而今忽弃去。想见处必益超诣。非常情所及。而不尔。无亦再数长廊柱之惑耶。恨无由与闻也。元行衰病日添。忧冗衮衮。古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者。未尝不三复而慨然也。不宣。与任仲思
黔院碑文曲折。想已经尊听。玆事体大。本非区区浅陋所敢当。念此非仲思笔力。无能以发挥。无论甲为乙为。惟善为则实为斯文公共之一幸事。计仲思于此必不存物我。幸为之命意措辞。略成一本见教。则窃欲依以为之。庶免致误大事。切乞不惜留神而亟就之。吾辈后学。于两宋先生受恩如何。可不共推血诚。自效于表章之万一乎。此非元行一人之私。实仲思之所宜乐闻也。千万恳祈。
与任仲思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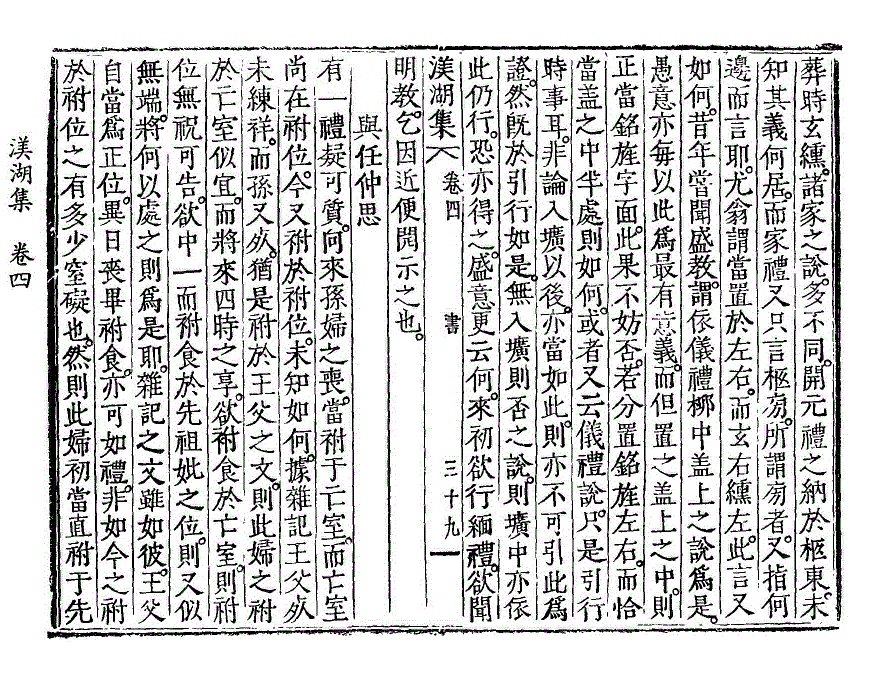 葬时玄纁。诸家之说。多不同。开元礼之纳于柩东。未知其义何居。而家礼又只言柩旁。所谓旁者。又指何边而言耶。尤翁谓当置于左右。而玄右纁左。此言又如何。昔年尝闻盛教。谓依仪礼柳中盖上之说为是。愚意亦每以此为最有意义。而但置之盖上之中。则正当铭旌字面。此果不妨否。若分置铭旌左右。而恰当盖之中半处则如何。或者又云仪礼说。只是引行时事耳。非论入圹以后。亦当如此。则亦不可引此为證。然既于引行如是。无入圹则否之说。则圹中亦依此仍行。恐亦得之。盛意更云何。来初欲行缅礼。欲闻明教。乞因近便开示之也。
葬时玄纁。诸家之说。多不同。开元礼之纳于柩东。未知其义何居。而家礼又只言柩旁。所谓旁者。又指何边而言耶。尤翁谓当置于左右。而玄右纁左。此言又如何。昔年尝闻盛教。谓依仪礼柳中盖上之说为是。愚意亦每以此为最有意义。而但置之盖上之中。则正当铭旌字面。此果不妨否。若分置铭旌左右。而恰当盖之中半处则如何。或者又云仪礼说。只是引行时事耳。非论入圹以后。亦当如此。则亦不可引此为證。然既于引行如是。无入圹则否之说。则圹中亦依此仍行。恐亦得之。盛意更云何。来初欲行缅礼。欲闻明教。乞因近便开示之也。与任仲思
有一礼疑可质。向来孙妇之丧。当祔于亡室。而亡室尚在祔位。今又祔于祔位。未知如何。据杂记王父死未练祥。而孙又死。犹是祔于王父之文。则此妇之祔于亡室似宜。而将来四时之享。欲祔食于亡室。则祔位无祝可告。欲中一而祔食于先祖妣之位。则又似无端。将何以处之则为是耶。杂记之文虽如彼。王父自当为正位。异日丧毕祔食。亦可如礼。非如今之祔于祔位之有多少窒碍也。然则此妇初当直祔于先
渼湖集卷之四 第 97L 页
 祖妣为得耶。望明教也。
祖妣为得耶。望明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