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x 页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书
书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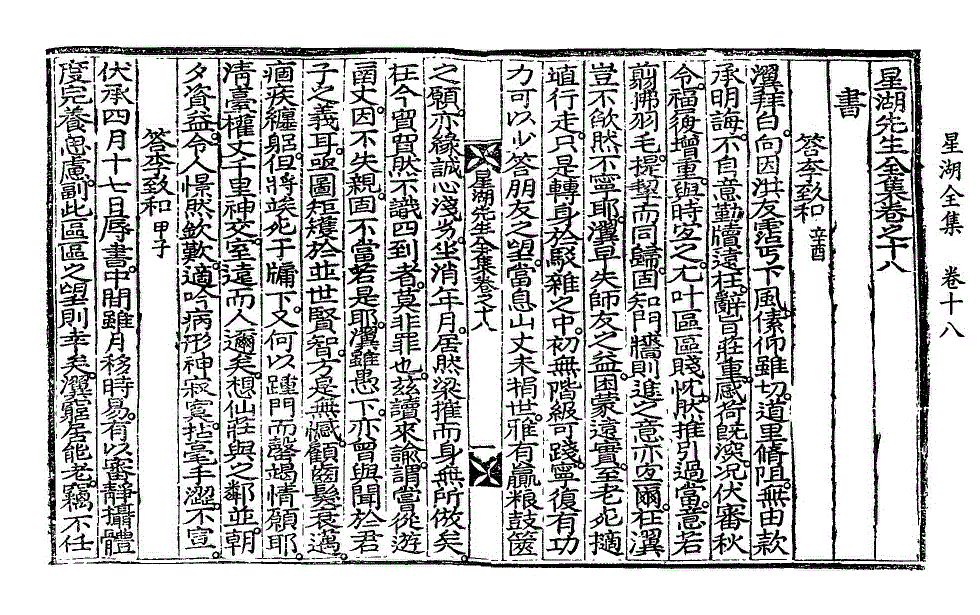 答李致和(辛酉)
答李致和(辛酉)瀷拜白。向因洪友沾丐下风。傃仰虽切。道里脩阻。无由款承明诲。不自意勤牍远在。辞旨庄重。感荷既深。况伏审秋令。福履增重。与时宜之。尤叶区区贱忱。然推引过当。意若剪拂羽毛。提挈而同归。固知门墙则进之意亦宜尔。在瀷岂不欿然不宁耶。瀷早失师友之益。困蒙远实。至老死擿埴行走。只是转身于驳杂之中。初无阶级可践。宁复有功力可以少答朋友之望。当息山丈未捐世。雅有赢粮鼓箧之愿。亦缘诚心浅劣。坐消年月。居然梁摧而身无所仿矣。在今贸贸然不识四到者。莫非罪也。玆读来谕。谓尝从游函丈。因不失亲。固不当若是耶。瀷虽愚下。亦曾与闻于君子之义耳。亟图矩矱于并世贤智。方是无憾。顾齿发衰迈。痼疾缠躬。但将俟死于牖下。又何以踵门而罄竭情愿耶。清台权丈千里神交。室远而人迩矣。想仙庄与之邻并。朝夕资益。令人憬然钦叹。适吟病形神寂寞。拈毫手涩。不宣。
答李致和(甲子)
伏承四月十七日辱书。中间虽月移时易。有以审静摄体度完养思虑。副此区区之望则幸矣。瀷穷居能老。窃不任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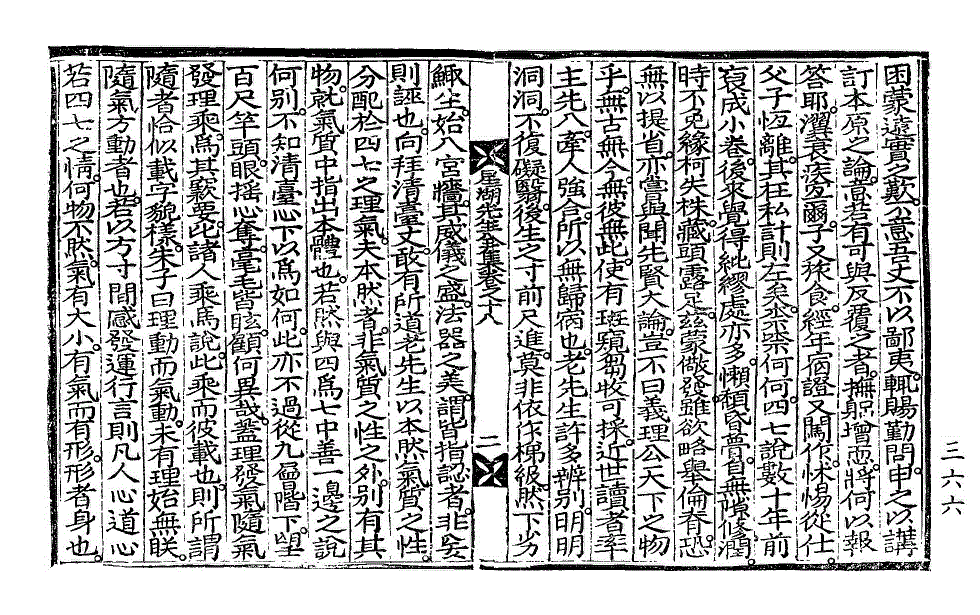 困蒙远实之叹。不意吾丈不以鄙夷。辄赐勤问。申之以讲订本原之论。意若有可与反覆之者。抚躬增恧。将何以报答耶。瀷衰疾宜尔。子又旅食。经年宿證又闯作。怵惕从仕。父子恒离。其在私计则左矣。柰柰何何。四七说数十年前裒成小卷。后来觉得纰缪处亦多。懒颓昏瞢。自无隙修润。时不免缘柯失株。藏头露足。玆蒙儆发。虽欲略举伦脊。恐无以提省。亦尝与闻先贤大论。岂不曰义理公天下之物乎。无古无今。无彼无此。使有斑窥刍牧可采。近世读者率主先入。牵人强合。所以无归宿也。老先生许多辨别。明明洞洞。不复碍翳。后生之寸前尺进。莫非依作梯级。然下劣鲰生。始入宫墙。其威仪之盛。法器之美。谓皆指认者。非妄则诬也。向拜清台丈。敢有所道老先生以本然气质之性。分配于四七之理气。夫本然者。非气质之性之外。别有其物。就气质中指出本体也。若然与四为七中善一边之说何别。不知清台心下以为如何。此亦不过从九层阶下。望百尺竿头。眼摇心夺。毫毛皆眩。顾何异哉。盖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为其窾要。比诸人乘马说。此乘而彼载也。则所谓随者恰似载字貌样。朱子曰理动而气动。未有理始无眹。随气方动者也。若以方寸间感发运行言则凡人心道心若四七之情。何物不然。气有大小。有气而有形。形者身也。
困蒙远实之叹。不意吾丈不以鄙夷。辄赐勤问。申之以讲订本原之论。意若有可与反覆之者。抚躬增恧。将何以报答耶。瀷衰疾宜尔。子又旅食。经年宿證又闯作。怵惕从仕。父子恒离。其在私计则左矣。柰柰何何。四七说数十年前裒成小卷。后来觉得纰缪处亦多。懒颓昏瞢。自无隙修润。时不免缘柯失株。藏头露足。玆蒙儆发。虽欲略举伦脊。恐无以提省。亦尝与闻先贤大论。岂不曰义理公天下之物乎。无古无今。无彼无此。使有斑窥刍牧可采。近世读者率主先入。牵人强合。所以无归宿也。老先生许多辨别。明明洞洞。不复碍翳。后生之寸前尺进。莫非依作梯级。然下劣鲰生。始入宫墙。其威仪之盛。法器之美。谓皆指认者。非妄则诬也。向拜清台丈。敢有所道老先生以本然气质之性。分配于四七之理气。夫本然者。非气质之性之外。别有其物。就气质中指出本体也。若然与四为七中善一边之说何别。不知清台心下以为如何。此亦不过从九层阶下。望百尺竿头。眼摇心夺。毫毛皆眩。顾何异哉。盖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为其窾要。比诸人乘马说。此乘而彼载也。则所谓随者恰似载字貌样。朱子曰理动而气动。未有理始无眹。随气方动者也。若以方寸间感发运行言则凡人心道心若四七之情。何物不然。气有大小。有气而有形。形者身也。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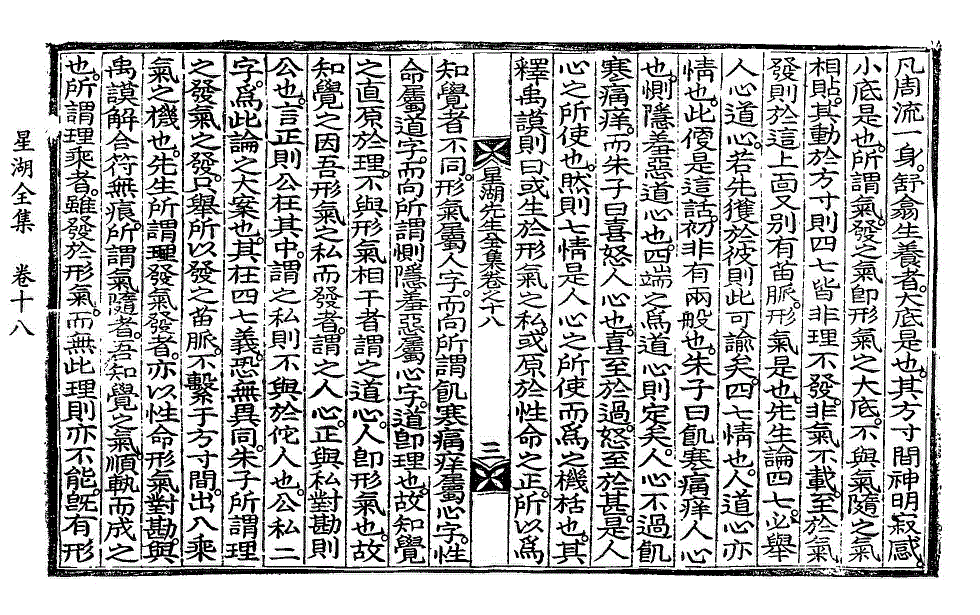 凡周流一身。舒翕生养者。大底是也。其方寸间神明寂感。小底是也。所谓气。发之气即形气之大底。不与气随之气相贴。其动于方寸则四七皆非理不发。非气不载。至于气发则于这上面又别有苗脉。形气是也。先生论四七。必举人心道心。若先获于彼则此可谕矣。四七情也。人道心亦情也。此便是这话。初非有两般也。朱子曰饥寒痛痒人心也。恻隐羞恶道心也。四端之为道心则定矣。人心不过饥寒痛痒。而朱子曰喜怒人心也。喜至于过。怒至于甚。是人心之所使也。然则七情是人心之所使而为之机栝也。其释禹谟则曰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形气属人字。而向所谓饥寒痛痒属心字。性命属道字。而向所谓恻隐羞恶属心字。道即理也。故知觉之直原于理。不与形气相干者谓之道心。人即形气也。故知觉之因吾形气之私而发者。谓之人心。正与私对勘则公也。言正则公在其中。谓之私则不与于佗人也。公私二字。为此论之大案也。其在四七义。恐无异同。朱子所谓理之发气之发。只举所以发之苗脉。不系于方寸间。出入乘气之机也。先生所谓理发气发者。亦以性命形气对勘。与禹谟解合符无痕。所谓气随者。吾知觉之气。顺轨而成之也。所谓理乘者。虽发于形气。而无此理则亦不能。既有形
凡周流一身。舒翕生养者。大底是也。其方寸间神明寂感。小底是也。所谓气。发之气即形气之大底。不与气随之气相贴。其动于方寸则四七皆非理不发。非气不载。至于气发则于这上面又别有苗脉。形气是也。先生论四七。必举人心道心。若先获于彼则此可谕矣。四七情也。人道心亦情也。此便是这话。初非有两般也。朱子曰饥寒痛痒人心也。恻隐羞恶道心也。四端之为道心则定矣。人心不过饥寒痛痒。而朱子曰喜怒人心也。喜至于过。怒至于甚。是人心之所使也。然则七情是人心之所使而为之机栝也。其释禹谟则曰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形气属人字。而向所谓饥寒痛痒属心字。性命属道字。而向所谓恻隐羞恶属心字。道即理也。故知觉之直原于理。不与形气相干者谓之道心。人即形气也。故知觉之因吾形气之私而发者。谓之人心。正与私对勘则公也。言正则公在其中。谓之私则不与于佗人也。公私二字。为此论之大案也。其在四七义。恐无异同。朱子所谓理之发气之发。只举所以发之苗脉。不系于方寸间。出入乘气之机也。先生所谓理发气发者。亦以性命形气对勘。与禹谟解合符无痕。所谓气随者。吾知觉之气。顺轨而成之也。所谓理乘者。虽发于形气。而无此理则亦不能。既有形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7L 页
 气。不食则饥不衣则寒。掐著痛爬著痒。是形气上所合有之心。言人心时犹不及于七情。既有这心。顺之则喜。拂之则怒。伤之则哀。威之则惧。亦必然之理也。此莫不有当然之则。无天理之裁制。便易危坠。若无七情之为之机栝则人心之所以为危者何也。故谓七情便是人心则可。若谓人心即七情则有违。凡大而禽兽细而虫豸。莫不具七情。其于四端则无迹也。是以拈公私二字。为判讼之案。而诸说之同异得失。可从此推去也。至于舜之怒孟子之喜。又别是一义。此惟圣贤有之。七情之说。昉于礼运。岂不曰七者不学而能乎。始知七情之本然。不离于私有也。亦不曰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乎。其本然则虽私而万物属己。明于其利。达于其患。不假于意之而必知其情。视天下之喜怒。把作己之喜怒。是圣贤之形气许大也。非七者之本公也。夫纵敌则敌喜。杀敌则敌怒。虽圣贤不与彼同。喜怒则亦可以左契矣。不能枚举。亦不敢终嘿。草草布此。可否惟命焉。朱子答汪叔耕书。以单传密付。论太极图者。深以为非。谓背形逐影。指妄为真。而先生之于辅庆源所记。亦下此句。其义何居。高峰后说。终不能脱然于旧套。又许以独见昭旷之源何也。此皆可讲者也。勉斋所谓理动气挟。气动理乘者。不曾见之。商其语理动气动。贴
气。不食则饥不衣则寒。掐著痛爬著痒。是形气上所合有之心。言人心时犹不及于七情。既有这心。顺之则喜。拂之则怒。伤之则哀。威之则惧。亦必然之理也。此莫不有当然之则。无天理之裁制。便易危坠。若无七情之为之机栝则人心之所以为危者何也。故谓七情便是人心则可。若谓人心即七情则有违。凡大而禽兽细而虫豸。莫不具七情。其于四端则无迹也。是以拈公私二字。为判讼之案。而诸说之同异得失。可从此推去也。至于舜之怒孟子之喜。又别是一义。此惟圣贤有之。七情之说。昉于礼运。岂不曰七者不学而能乎。始知七情之本然。不离于私有也。亦不曰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乎。其本然则虽私而万物属己。明于其利。达于其患。不假于意之而必知其情。视天下之喜怒。把作己之喜怒。是圣贤之形气许大也。非七者之本公也。夫纵敌则敌喜。杀敌则敌怒。虽圣贤不与彼同。喜怒则亦可以左契矣。不能枚举。亦不敢终嘿。草草布此。可否惟命焉。朱子答汪叔耕书。以单传密付。论太极图者。深以为非。谓背形逐影。指妄为真。而先生之于辅庆源所记。亦下此句。其义何居。高峰后说。终不能脱然于旧套。又许以独见昭旷之源何也。此皆可讲者也。勉斋所谓理动气挟。气动理乘者。不曾见之。商其语理动气动。贴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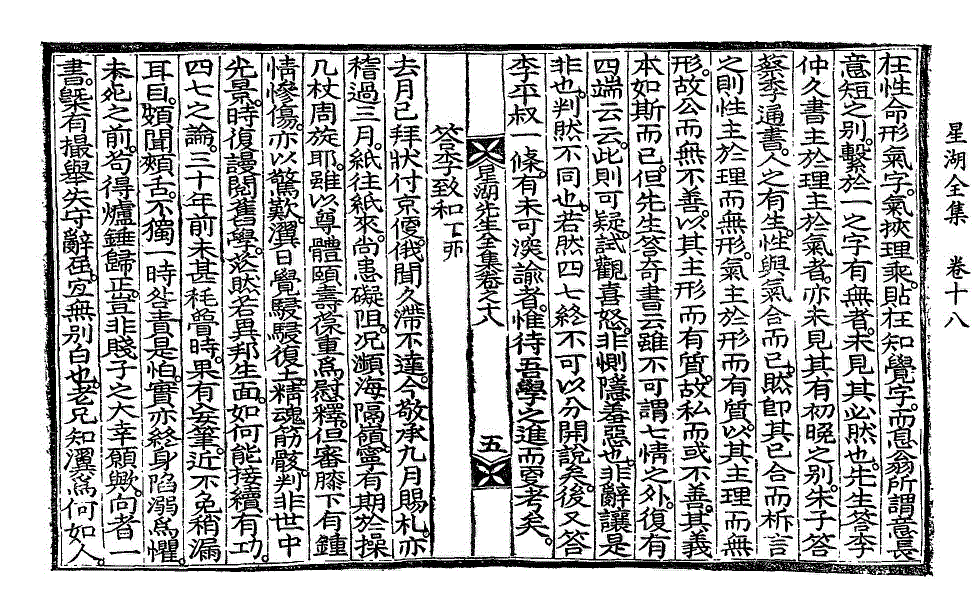 在性命形气字。气挟理乘。贴在知觉字。而息翁所谓意长意短之别。系于一之字有无者。未见其必然也。先生答李仲久书主于理主于气者。亦未见其有初晚之别。朱子答蔡季通书。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其义本如斯而已。但先生答奇书云虽不可谓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云云。此则可疑。试观喜怒。非恻隐羞恶也。非辞让是非也。判然不同也。若然四七终不可以分开说矣。后又答李平叔一条。有未可深谕者。惟待吾学之进而更考矣。
在性命形气字。气挟理乘。贴在知觉字。而息翁所谓意长意短之别。系于一之字有无者。未见其必然也。先生答李仲久书主于理主于气者。亦未见其有初晚之别。朱子答蔡季通书。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其义本如斯而已。但先生答奇书云虽不可谓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云云。此则可疑。试观喜怒。非恻隐羞恶也。非辞让是非也。判然不同也。若然四七终不可以分开说矣。后又答李平叔一条。有未可深谕者。惟待吾学之进而更考矣。答李致和(丁卯)
去月已拜状付京便。俄闻久滞不达。今敬承九月赐札。亦稽过三月。纸往纸来。尚患碍阻。况濒海隔岭。宁有期于操几杖周旋耶。虽以尊体颐寿葆重为慰释。但审膝下有钟情惨伤。亦以惊叹。瀷日觉骎骎复土。精魂筋骸。判非世中光景。时复谩阅旧学。茫然若异邦生面。如何能接续有功。四七之论。三十年前未甚秏瞢时。果有妄笔。近不免稍漏耳目。颇闻颊舌。不独一时咎责是怕。实亦终身陷溺为惧。未死之前。苟得炉锤归正。岂非贱子之大幸愿欤。向者一书。槩有撮举失守辞屈。宜无别白也。老兄知瀷为何如人。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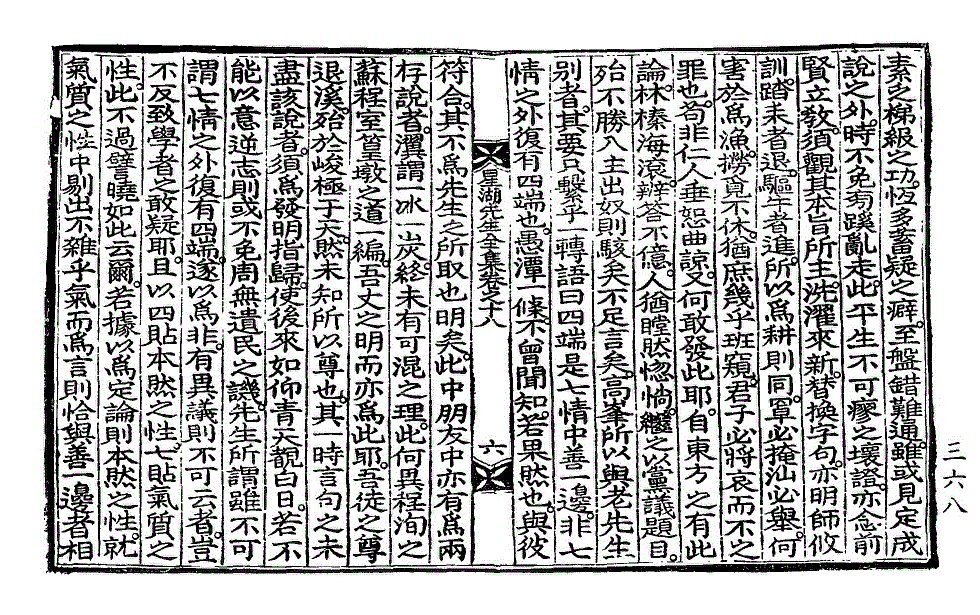 素乏梯级之功。恒多蓄疑之癖。至盘错难通。虽或见定成说之外。时不免旁蹊乱走。此平生不可瘳之坏證。亦念前贤立教。须观其本旨所主。洗濯来新。替换字句。亦明师攸训。踏耒者退。驱牛者进。所以为耕则同。罩必掩汕必举。何害于为渔。捞觅不休。犹庶几乎班窥。君子必将哀而不之罪也。苟非仁人垂恕曲谅。又何敢发此耶。自东方之有此论。林榛海滚。辨答不亿。人犹瞠然惚惝。继之以党议题目。殆不胜入主出奴则骇矣不足言矣。高峰所以与老先生别者。其要只系乎一转语曰四端是七情中善一边。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愚潭一条。不曾闻知。若果然也。与彼符合。其不为先生之所取也明矣。此中朋友中亦有为两存说者。瀷谓一冰一炭。终未有可混之理。此何异程洵之苏程室篁墩之道一编。吾丈之明而亦为此耶。吾徒之尊退溪。殆于峻极于天。然未知所以尊也。其一时言句之未尽该说者。须为发明指归。使后来如仰青天睹白日。若不能以意逆志则或不免周无遗民之讥。先生所谓虽不可谓七情之外复有四端。遂以为非。有异议则不可云者。岂不反致学者之敢疑耶。且以四贴本然之性。七贴气质之性。此不过譬晓如此云尔。若据以为定论则本然之性。就气质之性中剔出不杂乎气而为言则恰与善一边者相
素乏梯级之功。恒多蓄疑之癖。至盘错难通。虽或见定成说之外。时不免旁蹊乱走。此平生不可瘳之坏證。亦念前贤立教。须观其本旨所主。洗濯来新。替换字句。亦明师攸训。踏耒者退。驱牛者进。所以为耕则同。罩必掩汕必举。何害于为渔。捞觅不休。犹庶几乎班窥。君子必将哀而不之罪也。苟非仁人垂恕曲谅。又何敢发此耶。自东方之有此论。林榛海滚。辨答不亿。人犹瞠然惚惝。继之以党议题目。殆不胜入主出奴则骇矣不足言矣。高峰所以与老先生别者。其要只系乎一转语曰四端是七情中善一边。非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愚潭一条。不曾闻知。若果然也。与彼符合。其不为先生之所取也明矣。此中朋友中亦有为两存说者。瀷谓一冰一炭。终未有可混之理。此何异程洵之苏程室篁墩之道一编。吾丈之明而亦为此耶。吾徒之尊退溪。殆于峻极于天。然未知所以尊也。其一时言句之未尽该说者。须为发明指归。使后来如仰青天睹白日。若不能以意逆志则或不免周无遗民之讥。先生所谓虽不可谓七情之外复有四端。遂以为非。有异议则不可云者。岂不反致学者之敢疑耶。且以四贴本然之性。七贴气质之性。此不过譬晓如此云尔。若据以为定论则本然之性。就气质之性中剔出不杂乎气而为言则恰与善一边者相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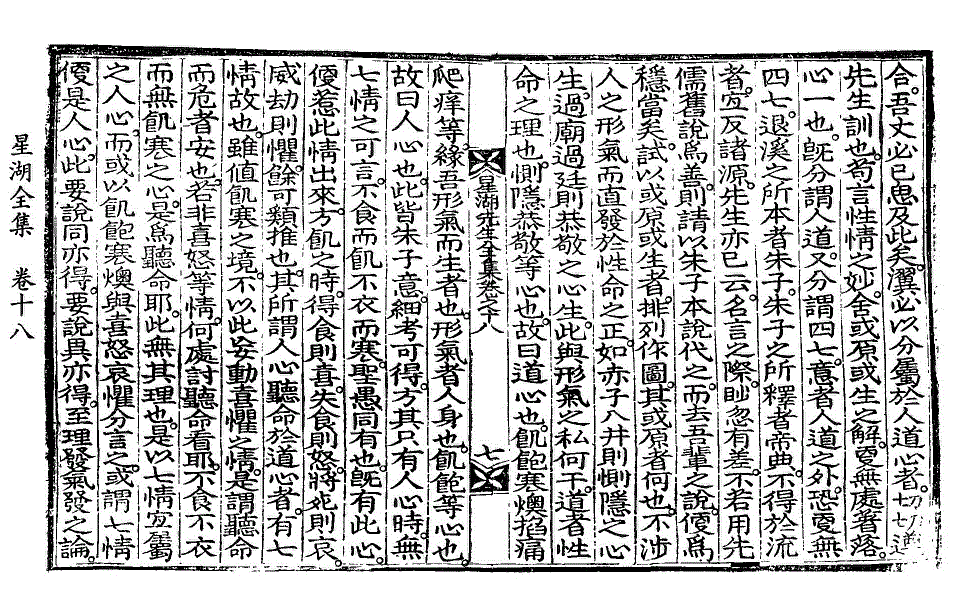 合。吾丈必已思及此矣。瀷必以分属于人道心者。切切遵先生训也。苟言性情之妙。舍或原或生之解。更无处著落。心一也。既分谓人道。又分谓四七。意者人道之外。恐更无四七。退溪之所本者朱子。朱子之所释者帝典。不得于流者。宜反诸源。先生亦已云。名言之际。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旧说为善。则请以朱子本说代之。而去吾辈之说。便为稳当矣。试以或原或生者。排列作图。其或原者何也。不涉人之形气而直发于性命之正。如赤子入井则恻隐之心生。过庙过廷则恭敬之心生。此与形气之私何干。道者性命之理也。恻隐恭敬等心也。故曰道心也。饥饱寒燠掐痛爬痒等。缘吾形气而生者也。形气者人身也。饥饱等心也。故曰人心也。此皆朱子意。细考可得。方其只有人心时。无七情之可言。不食而饥不衣而寒。圣愚同有也。既有此心。便惹此情出来。方饥之时。得食则喜。失食则怒。将死则哀。威劫则惧。馀可类推也。其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者。有七情故也。虽值饥寒之境。不以此妄动喜惧之情。是谓听命而危者安也。若非喜怒等情。何处讨听命看耶。不食不衣而无饥寒之心。是为听命耶。此无其理也。是以七情宜属之人心。而或以饥饱寒燠与喜怒哀惧分言之。或谓七情便是人心。此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至理发气发之论。
合。吾丈必已思及此矣。瀷必以分属于人道心者。切切遵先生训也。苟言性情之妙。舍或原或生之解。更无处著落。心一也。既分谓人道。又分谓四七。意者人道之外。恐更无四七。退溪之所本者朱子。朱子之所释者帝典。不得于流者。宜反诸源。先生亦已云。名言之际。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旧说为善。则请以朱子本说代之。而去吾辈之说。便为稳当矣。试以或原或生者。排列作图。其或原者何也。不涉人之形气而直发于性命之正。如赤子入井则恻隐之心生。过庙过廷则恭敬之心生。此与形气之私何干。道者性命之理也。恻隐恭敬等心也。故曰道心也。饥饱寒燠掐痛爬痒等。缘吾形气而生者也。形气者人身也。饥饱等心也。故曰人心也。此皆朱子意。细考可得。方其只有人心时。无七情之可言。不食而饥不衣而寒。圣愚同有也。既有此心。便惹此情出来。方饥之时。得食则喜。失食则怒。将死则哀。威劫则惧。馀可类推也。其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者。有七情故也。虽值饥寒之境。不以此妄动喜惧之情。是谓听命而危者安也。若非喜怒等情。何处讨听命看耶。不食不衣而无饥寒之心。是为听命耶。此无其理也。是以七情宜属之人心。而或以饥饱寒燠与喜怒哀惧分言之。或谓七情便是人心。此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至理发气发之论。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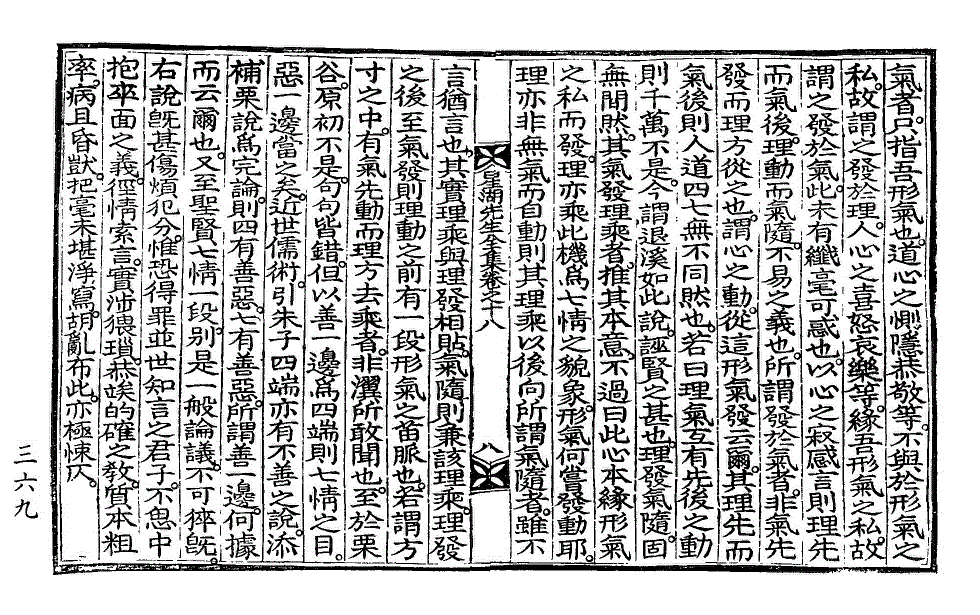 气者。只指吾形气也。道心之恻隐恭敬等。不与于形气之私。故谓之发于理。人心之喜怒哀乐等。缘吾形气之私。故谓之发于气。此未有纤毫可惑也。以心之寂感言则理先而气后。理动而气随。不易之义也。所谓发于气者。非气先发而理方从之也。谓心之动。从这形气发云尔。其理先而气后则人道四七无不同然也。若曰理气互有先后之动则千万不是。今谓退溪如此说。诬贤之甚也。理发气随。固无间然。其气发理乘者。推其本意。不过曰此心本缘形气之私而发。理亦乘此机为七情之貌象。形气何尝发动耶。理亦非无气而自动则其理乘以后向所谓气随者。虽不言犹言也。其实理乘与理发相贴。气随则兼该理乘。理发之后至气发则理动之前有一段形气之苗脉也。若谓方寸之中。有气先动而理方去乘者。非瀷所敢闻也。至于栗谷。原初不是。句句皆错。但以善一边为四端则七情之目。恶一边当之矣。近世儒术。引朱子四端亦有不善之说。添补栗说为完论。则四有善恶。七有善恶。所谓善一边。何据而云尔也。又至圣贤七情一段。别是一般论议。不可猝既。右说既甚伤烦犯分。惟恐得罪并世知言之君子。不思中抱卒面之义。径情索言。实涉猥琐。恭俟的确之教。质本粗率。病且昏呆。把毫未堪净写。胡乱布此。亦极悚仄。
气者。只指吾形气也。道心之恻隐恭敬等。不与于形气之私。故谓之发于理。人心之喜怒哀乐等。缘吾形气之私。故谓之发于气。此未有纤毫可惑也。以心之寂感言则理先而气后。理动而气随。不易之义也。所谓发于气者。非气先发而理方从之也。谓心之动。从这形气发云尔。其理先而气后则人道四七无不同然也。若曰理气互有先后之动则千万不是。今谓退溪如此说。诬贤之甚也。理发气随。固无间然。其气发理乘者。推其本意。不过曰此心本缘形气之私而发。理亦乘此机为七情之貌象。形气何尝发动耶。理亦非无气而自动则其理乘以后向所谓气随者。虽不言犹言也。其实理乘与理发相贴。气随则兼该理乘。理发之后至气发则理动之前有一段形气之苗脉也。若谓方寸之中。有气先动而理方去乘者。非瀷所敢闻也。至于栗谷。原初不是。句句皆错。但以善一边为四端则七情之目。恶一边当之矣。近世儒术。引朱子四端亦有不善之说。添补栗说为完论。则四有善恶。七有善恶。所谓善一边。何据而云尔也。又至圣贤七情一段。别是一般论议。不可猝既。右说既甚伤烦犯分。惟恐得罪并世知言之君子。不思中抱卒面之义。径情索言。实涉猥琐。恭俟的确之教。质本粗率。病且昏呆。把毫未堪净写。胡乱布此。亦极悚仄。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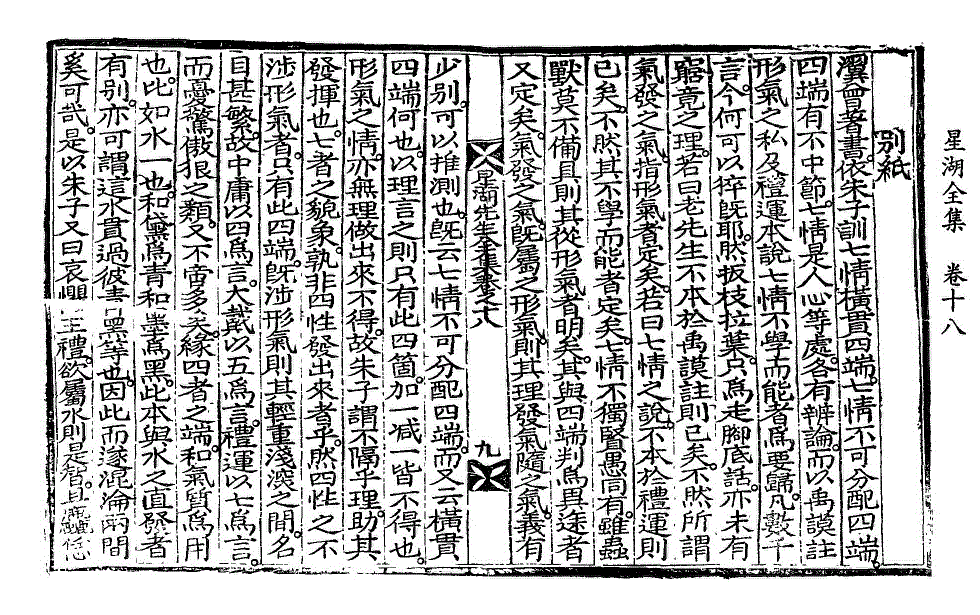 别纸
别纸瀷曾著书。依朱子训七情横贯四端。七情不可分配四端。四端有不中节。七情是人心等处。各有辨论。而以禹谟注形气之私及礼运本说七情不学而能者为要归。凡数千言。今何可以猝既耶。然扳枝拉叶。只为走脚底话。亦未有穷竟之理。若曰老先生不本于禹谟注则已矣。不然所谓气发之气。指形气者定矣。若曰七情之说。不本于礼运则已矣。不然其不学而能者定矣。七情不独贤愚同有。虽虫兽莫不备具则其从形气者明矣。其与四端判为异途者又定矣。气发之气。既属之形气。则其理发气随之气。义有少别。可以推测也。既云七情不可分配四端。而又云横贯四端何也。以理言之则只有此四个。加一减一皆不得也。形气之情。亦无理做出来不得。故朱子谓不隔乎理。助其发挥也。七者之貌象。孰非四性发出来者乎。然四性之不涉形气者。只有此四端。既涉形气则其轻重浅深之间。名目甚繁。故中庸以四为言。大戴以五为言。礼运以七为言。而忧惊傲狠之类。又不啻多矣。缘四者之端。和气质为用也。比如水一也。和黛为青和墨为黑。此本与水之直发者有别。亦可谓这水贯过彼青黑等也。因此而遂混沦两间奚可哉。是以朱子又曰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粗恁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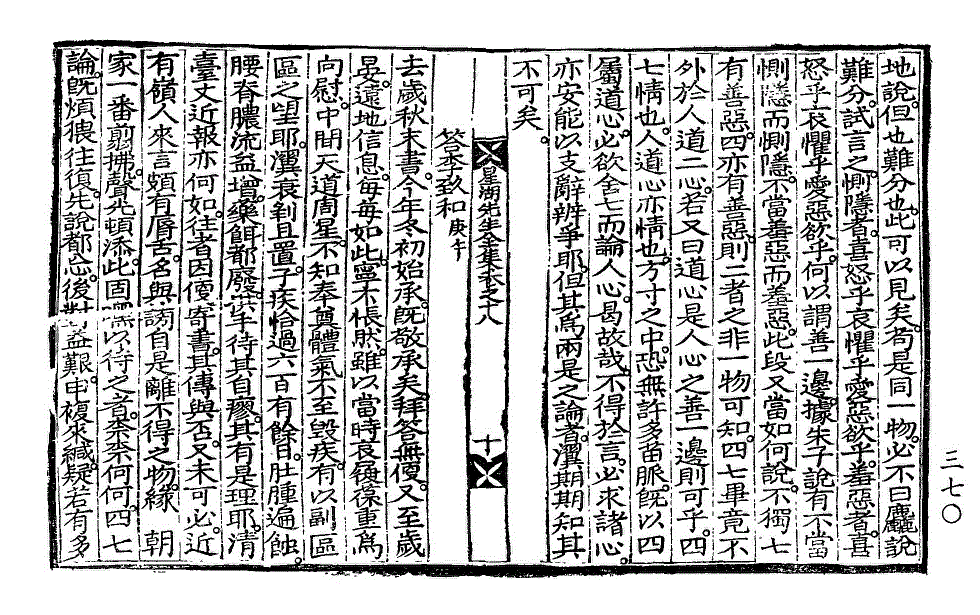 地说。但也难分也。此可以见矣。苟是同一物。必不曰粗说难分。试言之。恻隐者。喜怒乎哀惧乎爱恶欲乎。羞恶者。喜怒乎哀惧乎爱恶欲乎。何以谓善一边。据朱子说有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此段又当如何说。不独七有善恶。四亦有善恶。则二者之非一物可知。四七毕竟不外于人道二心。若又曰道心是人心之善一边则可乎。四七情也。人道心亦情也。方寸之中。恐无许多苗脉。既以四属道心。必欲舍七而论人心。曷故哉。不得于言。必求诸心。亦安能以支辞辨争耶。但其为两是之论者。瀷期期知其不可矣。
地说。但也难分也。此可以见矣。苟是同一物。必不曰粗说难分。试言之。恻隐者。喜怒乎哀惧乎爱恶欲乎。羞恶者。喜怒乎哀惧乎爱恶欲乎。何以谓善一边。据朱子说有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羞恶而羞恶。此段又当如何说。不独七有善恶。四亦有善恶。则二者之非一物可知。四七毕竟不外于人道二心。若又曰道心是人心之善一边则可乎。四七情也。人道心亦情也。方寸之中。恐无许多苗脉。既以四属道心。必欲舍七而论人心。曷故哉。不得于言。必求诸心。亦安能以支辞辨争耶。但其为两是之论者。瀷期期知其不可矣。答李致和(庚午)
去岁秋末书。今年冬初始承。既敬承矣。拜答无便。又至岁晏。远地信息。每每如此。宁不怅然。虽以当时哀履葆重为向慰。中间天道周星。不知奉奠体气不至毁疾。有以副区区之望耶。瀷衰剥且置。子疾恰过六百有馀日。肚肿遍蚀。腰脊脓流益增。药饵都废。拱手待其自瘳。其有是理耶。清台丈近报亦何如。往者因便寄书。其传与否。又未可必。近有岭人来言颇有唇舌。名与谤自是离不得之物。缘 朝家一番剪拂。声光顿添。此固嘿以待之者。柰柰何何。四七论。既烦猥往复。先说都忘。后对益艰。申复来缄。疑若有多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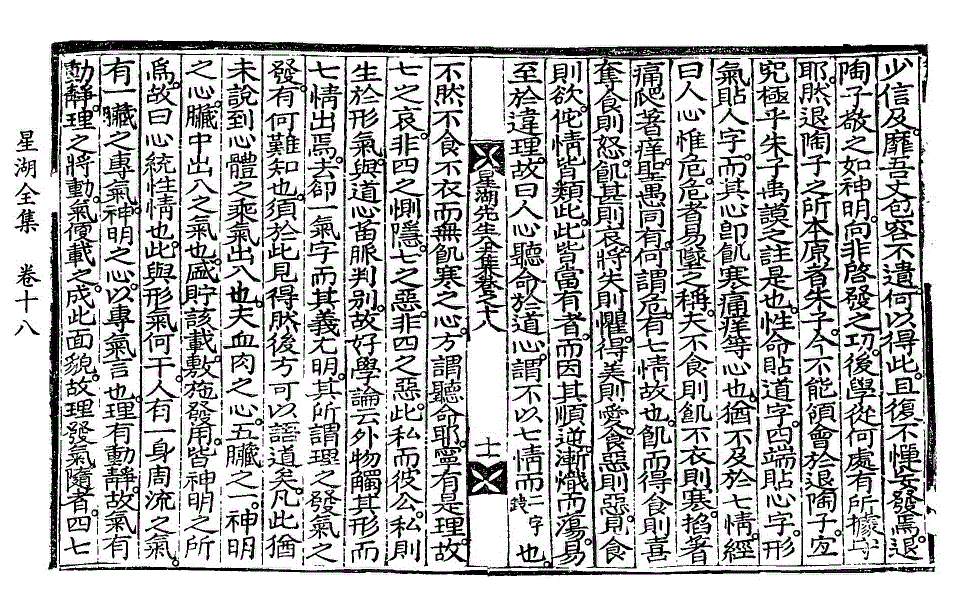 少信及。靡吾丈包容不遗。何以得此。且复不惮妄发焉。退陶子敬之如神明。向非启发之功。后学从何处有所据守耶。然退陶子之所本原者朱子。今不能领会于退陶子。宜究极乎朱子禹谟之注是也。性命贴道字。四端贴心字。形气贴人字。而其心即饥寒痛痒等心也。犹不及于七情。经曰人心惟危。危者易坠之称。夫不食则饥不衣则寒。掐著痛爬著痒。圣愚同有。何谓危。有七情故也。饥而得食则喜夺食则怒。饥甚则哀。将失则惧。得美则爱。食恶则恶。见食则欲。佗情皆类此。此皆当有者。而因其顺逆。渐炽而荡。易至于违理。故曰人心听命于道心。谓不以七情而(二字缺)也。不然不食不衣而无饥寒之心。方谓听命耶。宁有是理。故七之哀。非四之恻隐。七之恶。非四之恶。此私而彼公。私则生于形气。与道心苗脉判别。故好学论云外物触其形而七情出焉。去却一气字而其义尤明。其所谓理之发气之发。有何难知也。须于此见得然后方可以语道矣。凡此犹未说到心体之乘气出入也。夫血肉之心。五脏之一。神明之心。脏中出入之气也。盛贮该载。敷施发用。皆神明之所为。故曰心统性情也。此与形气何干。人有一身周流之气。有一脏之专气。神明之心。以专气言也。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理之将动。气便载之。成此面貌。故理发气随者。四七
少信及。靡吾丈包容不遗。何以得此。且复不惮妄发焉。退陶子敬之如神明。向非启发之功。后学从何处有所据守耶。然退陶子之所本原者朱子。今不能领会于退陶子。宜究极乎朱子禹谟之注是也。性命贴道字。四端贴心字。形气贴人字。而其心即饥寒痛痒等心也。犹不及于七情。经曰人心惟危。危者易坠之称。夫不食则饥不衣则寒。掐著痛爬著痒。圣愚同有。何谓危。有七情故也。饥而得食则喜夺食则怒。饥甚则哀。将失则惧。得美则爱。食恶则恶。见食则欲。佗情皆类此。此皆当有者。而因其顺逆。渐炽而荡。易至于违理。故曰人心听命于道心。谓不以七情而(二字缺)也。不然不食不衣而无饥寒之心。方谓听命耶。宁有是理。故七之哀。非四之恻隐。七之恶。非四之恶。此私而彼公。私则生于形气。与道心苗脉判别。故好学论云外物触其形而七情出焉。去却一气字而其义尤明。其所谓理之发气之发。有何难知也。须于此见得然后方可以语道矣。凡此犹未说到心体之乘气出入也。夫血肉之心。五脏之一。神明之心。脏中出入之气也。盛贮该载。敷施发用。皆神明之所为。故曰心统性情也。此与形气何干。人有一身周流之气。有一脏之专气。神明之心。以专气言也。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理之将动。气便载之。成此面貌。故理发气随者。四七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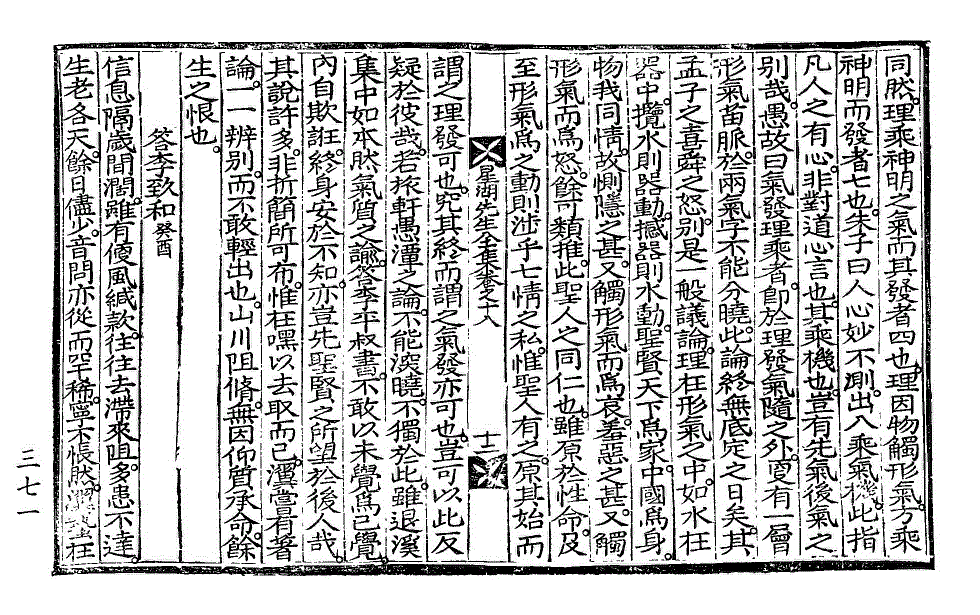 同然。理乘神明之气而其发者四也。理因物触形气。方乘神明而发者七也。朱子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此指凡人之有心。非对道心言也。其乘机也。岂有先气后气之别哉。愚故曰气发理乘者。即于理发气随之外。更有一层形气苗脉。于两气字不能分晓。此论终无底定之日矣。其孟子之喜舜之怒。别是一般议论。理在形气之中。如水在器中。揽水则器动。撼器则水动。圣贤天下为家。中国为身。物我同情。故恻隐之甚。又触形气而为哀。羞恶之甚。又触形气而为怒。馀可类推。此圣人之同仁也。虽原于性命。及至形气为之动则涉乎七情之私。惟圣人有之。原其始而谓之理发可也。究其终而谓之气发亦可也。岂可以此反疑于彼哉。若旅轩愚潭之论。不能深晓。不独于此。虽退溪集中如本然气质之谕。答李平叔书。不敢以未觉为已觉。内自欺诳。终身安于不知。亦岂先圣贤之所望于后人哉。其说许多。非折简所可布。惟在嘿以去取而已。瀷尝有著论。一一辨别。而不敢轻出也。山川阻脩。无因仰质承命。馀生之恨也。
同然。理乘神明之气而其发者四也。理因物触形气。方乘神明而发者七也。朱子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此指凡人之有心。非对道心言也。其乘机也。岂有先气后气之别哉。愚故曰气发理乘者。即于理发气随之外。更有一层形气苗脉。于两气字不能分晓。此论终无底定之日矣。其孟子之喜舜之怒。别是一般议论。理在形气之中。如水在器中。揽水则器动。撼器则水动。圣贤天下为家。中国为身。物我同情。故恻隐之甚。又触形气而为哀。羞恶之甚。又触形气而为怒。馀可类推。此圣人之同仁也。虽原于性命。及至形气为之动则涉乎七情之私。惟圣人有之。原其始而谓之理发可也。究其终而谓之气发亦可也。岂可以此反疑于彼哉。若旅轩愚潭之论。不能深晓。不独于此。虽退溪集中如本然气质之谕。答李平叔书。不敢以未觉为已觉。内自欺诳。终身安于不知。亦岂先圣贤之所望于后人哉。其说许多。非折简所可布。惟在嘿以去取而已。瀷尝有著论。一一辨别。而不敢轻出也。山川阻脩。无因仰质承命。馀生之恨也。答李致和(癸酉)
信息隔岁间阔。虽有便风缄款。往往去滞来阻。多患不达。生老各天。馀日尽少。音问亦从而罕稀。宁不怅然。瀷蛰在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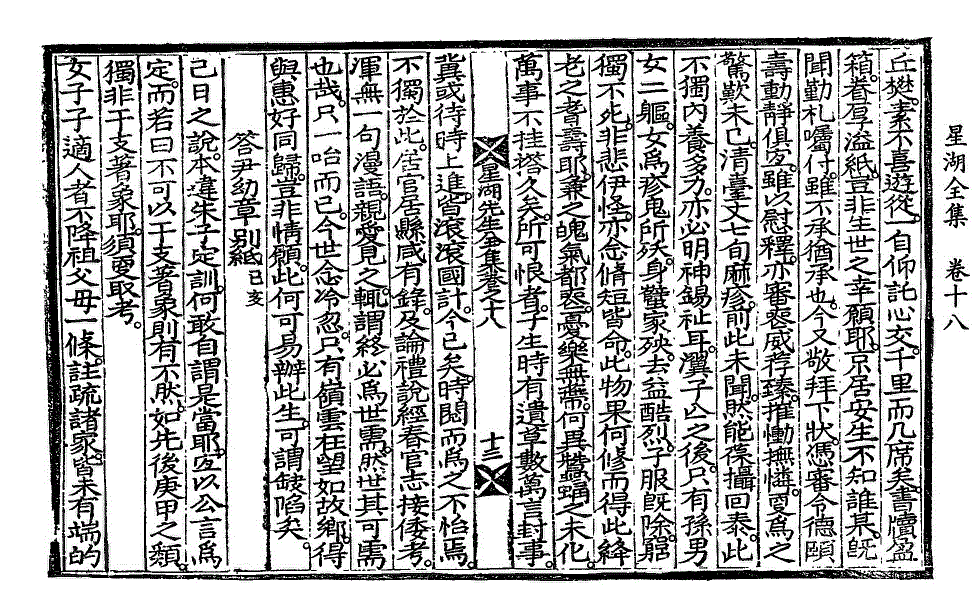 丘樊。素不喜游从。一自仰托心交。千里而几席矣。书牍盈箱。眷厚溢纸。岂非生世之幸愿耶。京居安生不知谁某。既闻勤札嘱付。虽不承犹承也。今又敬拜下状。凭审令德颐寿动静俱宜。虽以慰释。亦审丧威荐臻。摧恸抚怜。更为之惊叹未已。清台丈七旬麻疹。前此未闻。然能葆摄回泰。此不独内养多力。亦必明神锡祉耳。瀷子亡之后。只有孙男女二躯。女为疹鬼所夭。身蠥家殃。去益酷烈。子服既除。穷独不死。非悲伊怪。亦念脩短皆命。此物果何修而得此绛老之耆寿耶。兼之魄气都丧。忧乐无蒂。何异蚕蛹之未化。万事不挂搭久矣。所可恨者。子生时有遗草数万言封事。冀或待时上进。皆滚滚国计。今已矣。时阅而为之不怡焉。不独于此。居官居县咸有录。及论礼说经春官志接倭考。浑无一句漫语。亲爱见之。辄谓终必为世需。然世其可需也哉。只一咍而已。今世念冷忽。只有岭云在望如故乡。得与惠好同归。岂非情愿。此何可易办此生。可谓缺陷矣。
丘樊。素不喜游从。一自仰托心交。千里而几席矣。书牍盈箱。眷厚溢纸。岂非生世之幸愿耶。京居安生不知谁某。既闻勤札嘱付。虽不承犹承也。今又敬拜下状。凭审令德颐寿动静俱宜。虽以慰释。亦审丧威荐臻。摧恸抚怜。更为之惊叹未已。清台丈七旬麻疹。前此未闻。然能葆摄回泰。此不独内养多力。亦必明神锡祉耳。瀷子亡之后。只有孙男女二躯。女为疹鬼所夭。身蠥家殃。去益酷烈。子服既除。穷独不死。非悲伊怪。亦念脩短皆命。此物果何修而得此绛老之耆寿耶。兼之魄气都丧。忧乐无蒂。何异蚕蛹之未化。万事不挂搭久矣。所可恨者。子生时有遗草数万言封事。冀或待时上进。皆滚滚国计。今已矣。时阅而为之不怡焉。不独于此。居官居县咸有录。及论礼说经春官志接倭考。浑无一句漫语。亲爱见之。辄谓终必为世需。然世其可需也哉。只一咍而已。今世念冷忽。只有岭云在望如故乡。得与惠好同归。岂非情愿。此何可易办此生。可谓缺陷矣。答尹幼章别纸(己亥)
己日之说。本违朱子定训。何敢自谓是当耶。宜以公言为定。而若曰不可以干支著象则有不然。如先后庚甲之类。独非干支著象耶。须更取考。
女子子适人者不降祖父母一条。注疏诸家。皆未有端的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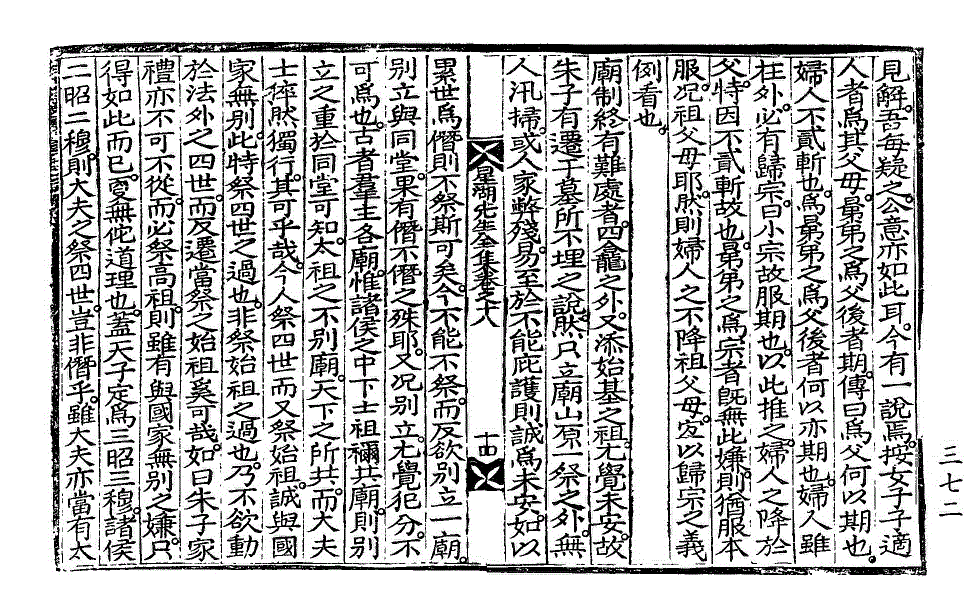 见解。吾每疑之。公意亦如此耳。今有一说焉。按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期。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何以亦期也。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故服期也。以此推之。妇人之降于父。特因不贰斩故也。昆弟之为宗者既无此嫌。则犹服本服。况祖父母耶。然则妇人之不降祖父母。宜以归宗之义例看也。
见解。吾每疑之。公意亦如此耳。今有一说焉。按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期。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何以亦期也。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故服期也。以此推之。妇人之降于父。特因不贰斩故也。昆弟之为宗者既无此嫌。则犹服本服。况祖父母耶。然则妇人之不降祖父母。宜以归宗之义例看也。庙制终有难处者。四龛之外。又添始基之祖。尤觉未安。故朱子有迁于墓所不埋之说。然只立庙山原一祭之外。无人汛扫。或人家弊残。易至于不能庇护则诚为未安。如以累世为僭则不祭斯可矣。今不能不祭。而反欲别立一庙。别立与同堂。果有僭不僭之殊耶。又况别立。尤觉犯分。不可为也。古者群主各庙。惟诸侯之中下士祖祢共庙。则别立之重于同堂可知。太祖之不别庙。天下之所共。而大夫士猝然独行。其可乎哉。今人祭四世而又祭始祖。诚与国家无别。此特祭四世之过也。非祭始祖之过也。乃不欲动于法外之四世。而反迁当祭之始祖奚可哉。如曰朱子家礼亦不可不从。而必祭高祖。则虽有与国家无别之嫌。只得如此而已。更无佗道理也。盖天子定为三昭三穆。诸侯二昭二穆。则大夫之祭四世。岂非僭乎。虽大夫亦当有太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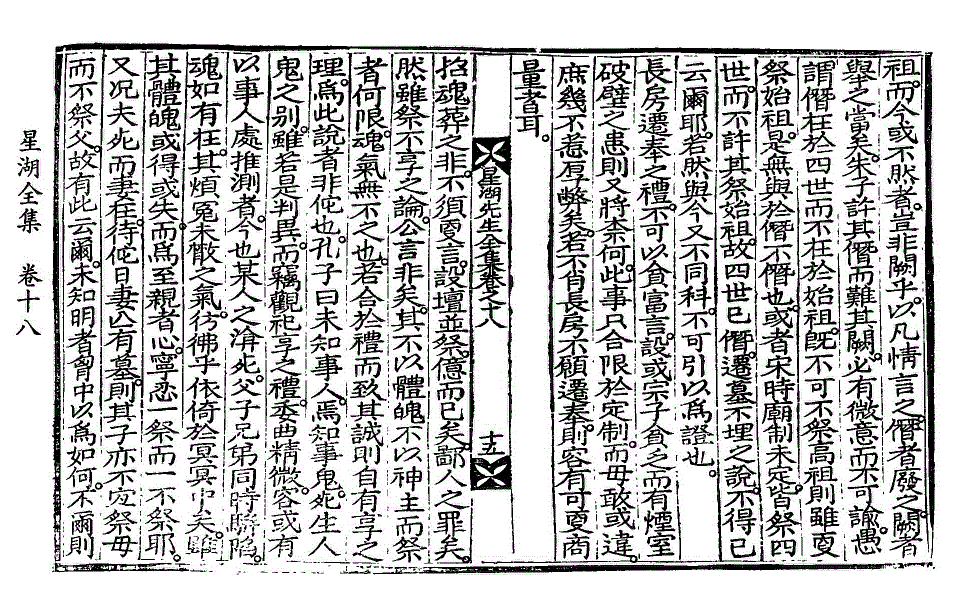 祖。而今或不然者。岂非阙乎。以凡情言之。僭者废之。阙者举之当矣。朱子许其僭而难其阙。必有微意而不可谕。愚谓僭在于四世而不在于始祖。既不可不祭高祖则虽更祭始祖。是无与于僭不僭也。或者宋时庙制未定。皆祭四世。而不许其祭始祖。故四世已僭。迁墓不埋之说。不得已云尔耶。若然与今又不同科。不可引以为證也。
祖。而今或不然者。岂非阙乎。以凡情言之。僭者废之。阙者举之当矣。朱子许其僭而难其阙。必有微意而不可谕。愚谓僭在于四世而不在于始祖。既不可不祭高祖则虽更祭始祖。是无与于僭不僭也。或者宋时庙制未定。皆祭四世。而不许其祭始祖。故四世已僭。迁墓不埋之说。不得已云尔耶。若然与今又不同科。不可引以为證也。长房迁奉之礼。不可以贫富言。设或宗子贫乏而有烟室破壁之患则又将柰何。此事只合限于定制。而毋敢或违。庶几不惹厚弊矣。若不肖长房不愿迁奉。则容有可更商量者耳。
招魂葬之非。不须更言。设坛并祭。亿而已矣。鄙人之罪矣。然虽祭不享之论。公言非矣。其不以体魄不以神主而祭者何限。魂气无不之也。若合于礼而致其诚则自有享之理。为此说者非佗也。孔子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死生人鬼之别。虽若是判异。而窃观祀享之礼。委曲精微。容或有以事人处推测者。今也某人之渰死。父子兄弟同时骈陷。魂如有在。其烦冤未散之气。彷佛乎依倚于冥冥中矣。虽其体魄或得或失。而为至亲者心。宁忍一祭而一不祭耶。又况夫死而妻在。待佗日妻亡有墓。则其子亦不宜祭母而不祭父。故有此云尔。未知明者胸中以为如何。不尔则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3L 页
 又有一说。虽不得其体魄。要必在此江中。即用望墓为坛之例于近江僻静处。为一坛场而祭之。似未害于孝子之情也。比者自本家有书来问。以近世士大夫之多虚葬为例。此奚独士大夫之家有之。国家 宣靖两陵亦然也。国陵则本先有墓。而后为倭所发。既是积岁妥灵之所。则何可以一朝顿废。此不过如鄙人设坛之意。而至其必具棺椁器物则又未知其如何也。至于近世士大夫家所行则有异焉。其心诚谓人皆有墓。吾亲独无是。于孝子之情。岂不衋然伤恸哉。然无者不可为有。凡物皆然。况父母之体魄乎。此鄙人所以不敢变说。以循本家之志也。
又有一说。虽不得其体魄。要必在此江中。即用望墓为坛之例于近江僻静处。为一坛场而祭之。似未害于孝子之情也。比者自本家有书来问。以近世士大夫之多虚葬为例。此奚独士大夫之家有之。国家 宣靖两陵亦然也。国陵则本先有墓。而后为倭所发。既是积岁妥灵之所。则何可以一朝顿废。此不过如鄙人设坛之意。而至其必具棺椁器物则又未知其如何也。至于近世士大夫家所行则有异焉。其心诚谓人皆有墓。吾亲独无是。于孝子之情。岂不衋然伤恸哉。然无者不可为有。凡物皆然。况父母之体魄乎。此鄙人所以不敢变说。以循本家之志也。父子并亡。父有佗子而子无后则于父之神主。当题云显考。子某摄祀。待立适孙而改题焉。于子之神主。当以无后之例书之。亦待立后而改题焉。上一款则曾闻之堂兄。其说如此。
家礼依伊川主式。本不用显字。奚独告事祝然哉。家礼图云礼经及家礼旧本。于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间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显字可也。此用显字之始也。然今考家礼。并无皇字。或者新旧本之有异耶。据礼经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显考。与此说不合。且谓高祖之用显字。而不言曾祖以下乃禁用皇字。其义未可知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4H 页
 也。若于四世并书显字则实无所考。而今人家通用已久。不可猝改也。但于告事祝独书故字。又不可解。陷中则不书属称。故书故字。今既书属称而又书故字。与佗祝例不同。其或未及修润者耶。
也。若于四世并书显字则实无所考。而今人家通用已久。不可猝改也。但于告事祝独书故字。又不可解。陷中则不书属称。故书故字。今既书属称而又书故字。与佗祝例不同。其或未及修润者耶。详家礼本文则祠堂之名。不系乎庑之有无。公言是矣。
按礼葬日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及卒哭用刚日。柔阴而刚阳。柔取其静而刚取其动。以其将祔于祖。故取其动也。非有吉凶之异也。
按仪礼及家礼自祔以后称孝子。沙溪说是也。礼意本如此。必欲改称哀者何所据耶。但家礼书疏称孤哀。书疏是卒哭后事也。是甚可疑。以意臆之。或者人之书问为丧也。己亦叙其祸延哀恸之故。不得不尔也。家间虽有节次向吉之渐。而与人则乃最初问答也。故以初丧之礼处之。文子既祥而受吊则却深衣练冠垂涕洟。其义可推也。未知公意如何。
长房同奉迁主之说似然。
文质彬彬。方为得中。然救僿莫如忠。故其或继周者必将尚忠。其势然也。野人之从。非但为彼善于此。亦所存在此矣。盖忠则归俭。文则流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天下之不复治乎。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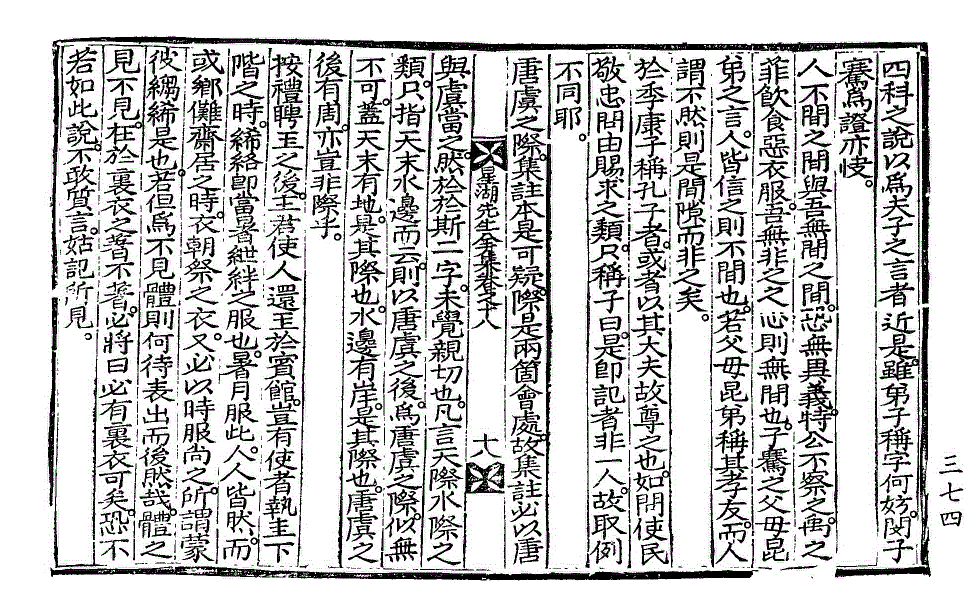 四科之说以为夫子之言者近是。虽弟子称字何妨。闵子骞为證亦快。
四科之说以为夫子之言者近是。虽弟子称字何妨。闵子骞为證亦快。人不间之间与吾无间之间。恐无异义。特公不察之。禹之菲饮食恶衣服。吾无非之之心则无间也。子骞之父母昆弟之言。人皆信之则不间也。若父母昆弟称其孝友。而人谓不然则是间隙而非之矣。
于季康子称孔子者。或者以其大夫故尊之也。如问使民敬忠问由赐求之类。只称子曰。是即记者非一人。故取例不同耶。
唐虞之际。集注本是可疑。际是两个会处。故集注必以唐与虞当之。然于于斯二字。未觉亲切也。凡言天际水际之类。只指天末水边而云。则以唐虞之后。为唐虞之际。似无不可。盖天末有地。是其际也。水边有岸。是其际也。唐虞之后有周。亦岂非际乎。
按礼聘玉之后。主君使人还玉于宾馆。岂有使者执圭下阶之时。絺络即当暑绁绊之服也。暑月服此。人人皆然。而或乡傩斋居之时。衣朝祭之衣。又必以时服尚之。所谓蒙彼绉絺是也。若但为不见体则何待表出而后然哉。体之见不见。在于里衣之著不著。必将曰必有里衣可矣。恐不若如此说。不敢质言。姑记所见。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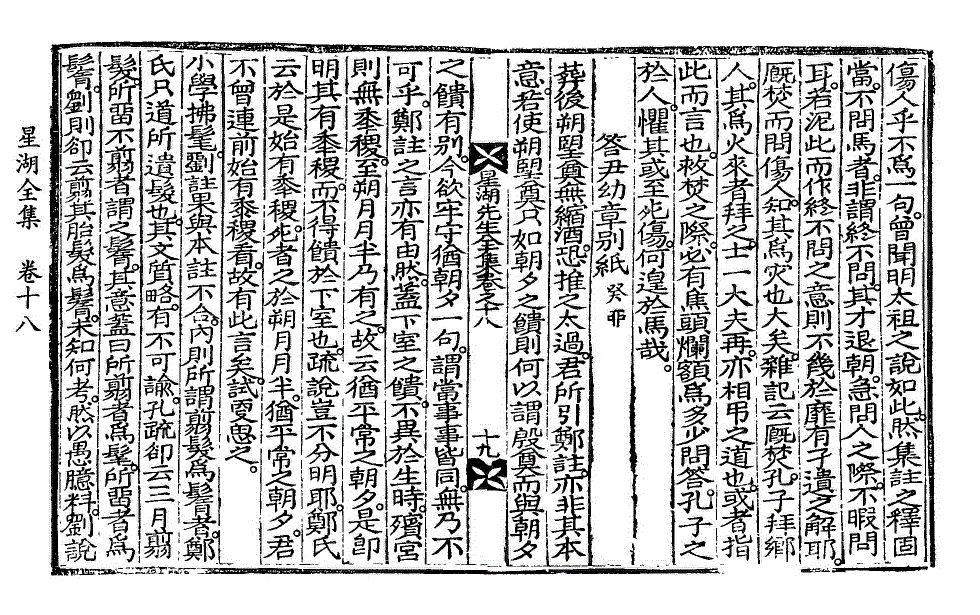 伤人乎不为一句。曾闻明太祖之说如此。然集注之释固当。不问马者。非谓终不问。其才退朝。急问人之际。不暇问耳。若泥此而作终不问之意则不几于靡有孑遗之解耶。厩焚而问伤人。知其为灾也大矣。杂记云厩焚。孔子拜乡人。其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或者指此而言也。救焚之际。必有焦头烂额为多少问答。孔子之于人。惧其或至死伤。何遑于马哉。
伤人乎不为一句。曾闻明太祖之说如此。然集注之释固当。不问马者。非谓终不问。其才退朝。急问人之际。不暇问耳。若泥此而作终不问之意则不几于靡有孑遗之解耶。厩焚而问伤人。知其为灾也大矣。杂记云厩焚。孔子拜乡人。其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或者指此而言也。救焚之际。必有焦头烂额为多少问答。孔子之于人。惧其或至死伤。何遑于马哉。答尹幼章别纸(癸卯)
葬后朔望奠无缩酒。恐推之太过。君所引郑注。亦非其本意。若使朔望奠只如朝夕之馈则何以谓殷奠而与朝夕之馈有别。今欲牢守犹朝夕一句。谓当事事皆同。无乃不可乎。郑注之言亦有由然。盖下室之馈。不异于生时。殡宫则无黍稷。至朔月月半乃有之。故云犹平常之朝夕。是即明其有黍稷。而不得馈于下室也。疏说岂不分明耶。郑氏云于是始有黍稷。死者之于朔月月半。犹平常之朝夕。君不曾连前始有黍稷看。故有此言矣。试更思之。
小学拂髦。刘注果与本注不合。内则所谓剪发为鬌者。郑氏只道所遗发也。其文质略。有不可谕。孔疏却云三月剪发。所留不剪者谓之鬌。其意盖曰所剪者为髦。所留者为鬌。刘则却云剪其胎发为鬌。未知何考。然以愚臆料。刘说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5L 页
 亦似近之。今观新生儿胎发极细短。浑头剪取。不满一撮。既剪则所留者几茎。而其能作鬌成样耶。儿生未半岁。胎发几乎尽落。假使为鬌。未及匍匐。鬌已去头。其留在头者不过日月间事。其有所益耶。且半岁之儿施鬌安用。是必不然矣。窃详郑氏之意。剪发一也。以幼时角羁于头者为鬌。既长有冠笄则饰而施于冠笄之上者为髦。鬌与髦异名则所饰必将异制。故曰其制未闻。非谓髦之发非鬌之发也。按士丧记既殡主人说髦。郑云儿生三月。剪发为鬌。长大犹为饰存之。谓之髦。此即分明指长大则加饰于鬌而为髦者也。此岂指当初剪发而所不剪者为鬌。及长则复以所剪者为髦之义耶。以郑證郑。亦甚明验。而但郑注拂髦云象幼时之鬌。此虽可疑。然彼既明證则此可以旁推。其意盖曰幼时有鬌。鬌有角羁之制。见于经。既冠笄则夹囟午达之制不复可用。故复饰为髦。以象幼时用鬌。而其制未闻也。饰既别矣。用既变矣。名亦改矣。以此象彼云者。固是无害。何必曰髦之发非鬌之发然后方成说耶。其曰所遗发者何也。郑意剪者非刀剪之义。故委曲解之也。儿生三月。气血未完。囟骨未合。于此刀剪其发。此不近理。至三月稍肥则胎发始有遗落者矣。剪字与剪本不同字。汇云羽毛摧落也。尔雅云剪齐也。或以摧落者为之。又或
亦似近之。今观新生儿胎发极细短。浑头剪取。不满一撮。既剪则所留者几茎。而其能作鬌成样耶。儿生未半岁。胎发几乎尽落。假使为鬌。未及匍匐。鬌已去头。其留在头者不过日月间事。其有所益耶。且半岁之儿施鬌安用。是必不然矣。窃详郑氏之意。剪发一也。以幼时角羁于头者为鬌。既长有冠笄则饰而施于冠笄之上者为髦。鬌与髦异名则所饰必将异制。故曰其制未闻。非谓髦之发非鬌之发也。按士丧记既殡主人说髦。郑云儿生三月。剪发为鬌。长大犹为饰存之。谓之髦。此即分明指长大则加饰于鬌而为髦者也。此岂指当初剪发而所不剪者为鬌。及长则复以所剪者为髦之义耶。以郑證郑。亦甚明验。而但郑注拂髦云象幼时之鬌。此虽可疑。然彼既明證则此可以旁推。其意盖曰幼时有鬌。鬌有角羁之制。见于经。既冠笄则夹囟午达之制不复可用。故复饰为髦。以象幼时用鬌。而其制未闻也。饰既别矣。用既变矣。名亦改矣。以此象彼云者。固是无害。何必曰髦之发非鬌之发然后方成说耶。其曰所遗发者何也。郑意剪者非刀剪之义。故委曲解之也。儿生三月。气血未完。囟骨未合。于此刀剪其发。此不近理。至三月稍肥则胎发始有遗落者矣。剪字与剪本不同字。汇云羽毛摧落也。尔雅云剪齐也。或以摧落者为之。又或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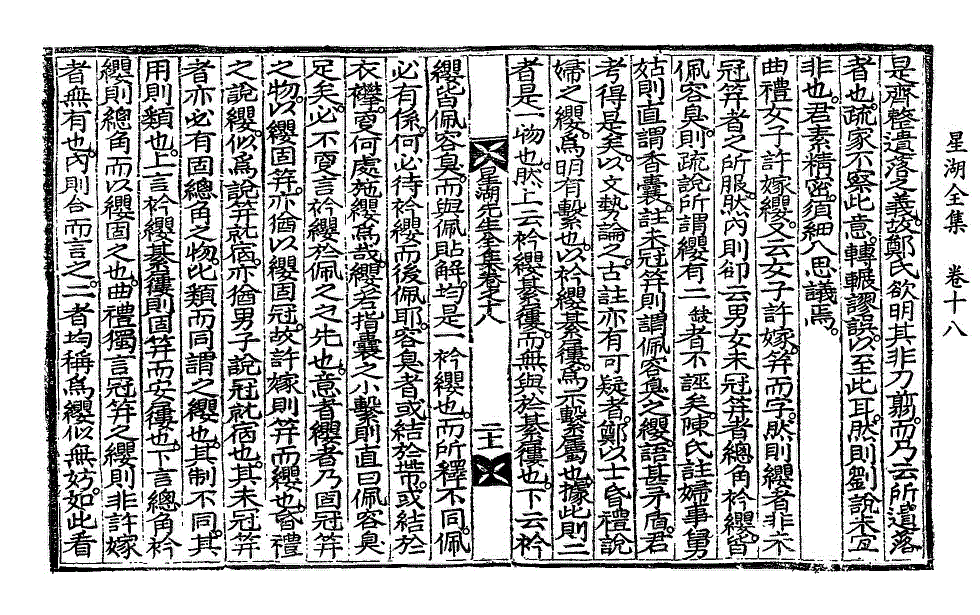 是齐整遗落之义。故郑氏欲明其非刀剪。而乃云所遗落者也。疏家不察此意。转辗谬误。以至此耳。然则刘说未宜非也。君素精密。须细入思议焉。
是齐整遗落之义。故郑氏欲明其非刀剪。而乃云所遗落者也。疏家不察此意。转辗谬误。以至此耳。然则刘说未宜非也。君素精密。须细入思议焉。曲礼女子许嫁缨。又云女子许嫁。笄而字。然则缨者非未冠笄者之所服。然内则却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则疏说所谓缨有二(缺)者不诬矣。陈氏注妇事舅姑则直谓香囊。注未冠笄则谓佩容臭之缨。语甚矛盾。君考得是矣。以文势论之。古注亦有可疑者。郑以士昏礼说妇之缨。为明有系也。以衿缨綦屦。为示系属也。据此则二者是一物也。然上云衿缨綦屦。而无与于綦屦也。下云衿缨皆佩容臭。而与佩贴解。均是一衿缨也。而所释不同。佩必有系。何必待衿缨而后佩耶。容臭者或结于带。或结于衣襻。更何处施缨为哉。缨若指囊之小系则直曰佩容臭足矣。必不更言衿缨于佩之之先也。意者缨者乃固冠笄之物。以缨固笄。亦犹以缨固冠。故许嫁则笄而缨也。昏礼之说缨。似为说笄就宿。亦犹男子说冠就宿也。其未冠笄者亦必有固总角之物。比类而同谓之缨也。其制不同。其用则类也。上言衿缨綦屦则固笄而安屦也。下言总角衿缨则总角而以缨固之也。曲礼独言冠笄之缨则非许嫁者无有也。内则合而言之。二者均称为缨似无妨。如此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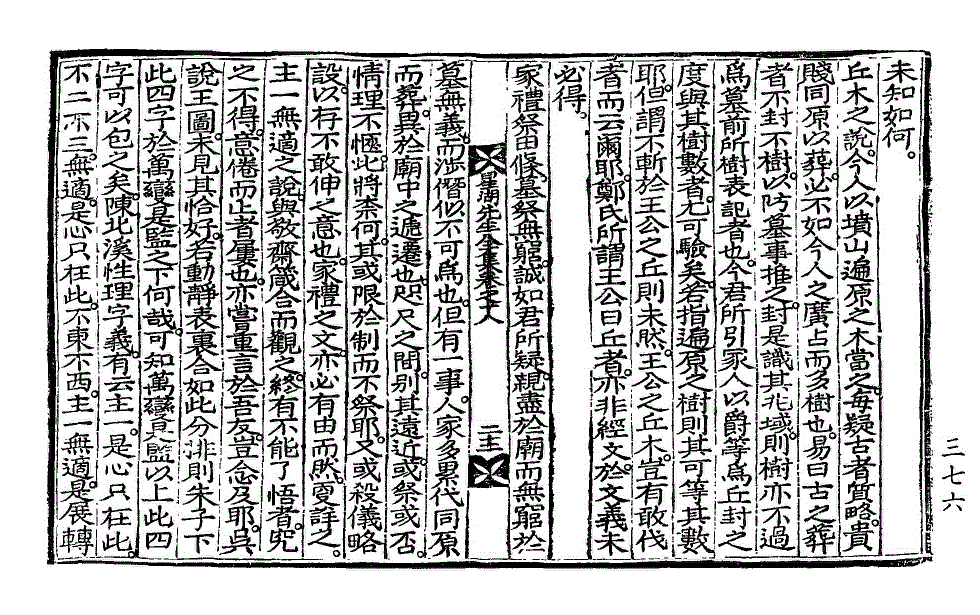 未知如何。
未知如何。丘木之说。今人以坟山遍原之木当之。每疑古者质略。贵贱同原以葬。必不如今人之广占而多树也。易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树。以防墓事推之。封是识其兆域。则树亦不过为墓前所树表记者也。今君所引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者。尤可验矣。若指遍原之树则其可等其数耶。但谓不斩于王公之丘则未然。王公之丘木。岂有敢伐者而云尔耶。郑氏所谓王公曰丘者。亦非经文。于文义未必得。
家礼祭田条。墓祭无穷。诚如君所疑。亲尽于庙而无穷于墓无义。而涉僭似不可为也。但有一事。人家多累代同原而葬。异于庙中之递迁也。咫尺之间。别其远近。或祭或否。情理不惬。此将柰何。其或限于制而不祭耶。又或杀仪略设。以存不敢伸之意也。家礼之文。亦必有由而然。更详之。主一无适之说。与敬斋箴合而观之。终有不能了悟者。究之不得。意倦而止者屡也。亦尝重言于吾友。岂念及耶。吴说王图。未见其恰好。若动静表里合如此分排则朱子下此四字于万变是监之下何哉。可知万变是监以上此四字可以包之矣。陈北溪性理字义。有云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无适。是心只在此。不东不西。主一无适。是展转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7H 页
 相解释要分明。非主一之外。又别有无适之功也。又曰无事时心常在里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时心应这事。更不张第二第三事来插也。是主一。北溪是朱门高等。必有所受之。此说更可商量也。其惟精之作惟心。若朱子大全及性理大全。分明如此。则彼心经何从而有是哉。诚可怪也。家中借来书。适皆无此卷。不能校检。然当从大全为是。考至此亦非细事。甚甚幸幸。大抵此箴多用古语。实如来教。专用精一之语。理似有之。设使其意义或有胜似者。孰敢妄易一字耶。君所改图。不宜率易。待后更评。其所引句语出处。君所录亦略备。试以所尝闻者添补之耳。法言云颜子涵心仲尼守口防意。虽出富郑公。其义又可详也。寒冈云瓶者所以储水。而恐其倾覆则守之宜不得不慎。城者所以防盗。而恐其疏缺则防之宜不得不密。此谓守人口如守瓶口也。左传昭公七年。谢息曰虽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礼也。注挈瓶汲者谕小智。为人守器。犹知不以借人。若用此语则谓当如小智之专心于守瓶也。然以防意如城者推之。不可作防城看则后说不精。朱子曰如瓶谨其出也。如城闲邪之入也。愚昔问此义于李松禾丈。李丈以小学非僻之心章方氏注曰心内也而言入何也。盖心虽在内。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则与之俱入矣。故得以入
相解释要分明。非主一之外。又别有无适之功也。又曰无事时心常在里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时心应这事。更不张第二第三事来插也。是主一。北溪是朱门高等。必有所受之。此说更可商量也。其惟精之作惟心。若朱子大全及性理大全。分明如此。则彼心经何从而有是哉。诚可怪也。家中借来书。适皆无此卷。不能校检。然当从大全为是。考至此亦非细事。甚甚幸幸。大抵此箴多用古语。实如来教。专用精一之语。理似有之。设使其意义或有胜似者。孰敢妄易一字耶。君所改图。不宜率易。待后更评。其所引句语出处。君所录亦略备。试以所尝闻者添补之耳。法言云颜子涵心仲尼守口防意。虽出富郑公。其义又可详也。寒冈云瓶者所以储水。而恐其倾覆则守之宜不得不慎。城者所以防盗。而恐其疏缺则防之宜不得不密。此谓守人口如守瓶口也。左传昭公七年。谢息曰虽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礼也。注挈瓶汲者谕小智。为人守器。犹知不以借人。若用此语则谓当如小智之专心于守瓶也。然以防意如城者推之。不可作防城看则后说不精。朱子曰如瓶谨其出也。如城闲邪之入也。愚昔问此义于李松禾丈。李丈以小学非僻之心章方氏注曰心内也而言入何也。盖心虽在内。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则与之俱入矣。故得以入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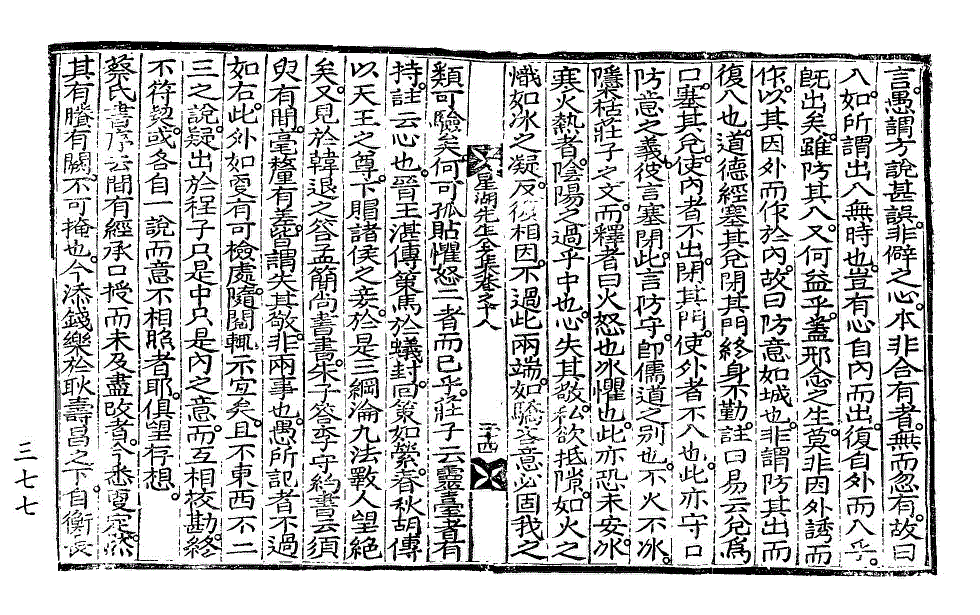 言。愚谓方说甚误。非僻之心。本非合有者。无而忽有。故曰入。如所谓出入无时也。岂有心自内而出。复自外而入乎。既出矣。虽防其入。又何益乎。盖邪念之生。莫非因外诱而作。以其因外而作于内。故曰防意如城也。非谓防其出而复入也。道德经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注曰易云兑为口。塞其兑。使内者不出。闭其门。使外者不入也。此亦守口防意之义。彼言塞闭。此言防守。即儒道之别也。不火不冰。檃栝庄子之文。而释者曰火怒也冰惧也。此亦恐未安。冰寒火热者。阴阳之过乎中也。心失其敬。私欲抵隙。如火之炽如冰之凝。反复相因。不过此两端。如骄吝意必固我之类可验矣。何可孤贴惧怒二者而已乎。庄子云灵台者有持。注云心也。晋王湛传策马于蚁封。回策如萦。春秋胡传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九法斁人望绝矣。又见于韩退之答孟简尚书书。朱子答李守约书云须臾有间。毫釐有差。皆谓失其敬。非两事也。愚所记者不过如右。此外如更有可检处。随阅辄示宜矣。且不东西不二三之说。疑出于程子只是中只是内之意。而互相校勘。终不符契。或各自一说而意不相照者耶。俱望存想。
言。愚谓方说甚误。非僻之心。本非合有者。无而忽有。故曰入。如所谓出入无时也。岂有心自内而出。复自外而入乎。既出矣。虽防其入。又何益乎。盖邪念之生。莫非因外诱而作。以其因外而作于内。故曰防意如城也。非谓防其出而复入也。道德经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注曰易云兑为口。塞其兑。使内者不出。闭其门。使外者不入也。此亦守口防意之义。彼言塞闭。此言防守。即儒道之别也。不火不冰。檃栝庄子之文。而释者曰火怒也冰惧也。此亦恐未安。冰寒火热者。阴阳之过乎中也。心失其敬。私欲抵隙。如火之炽如冰之凝。反复相因。不过此两端。如骄吝意必固我之类可验矣。何可孤贴惧怒二者而已乎。庄子云灵台者有持。注云心也。晋王湛传策马于蚁封。回策如萦。春秋胡传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九法斁人望绝矣。又见于韩退之答孟简尚书书。朱子答李守约书云须臾有间。毫釐有差。皆谓失其敬。非两事也。愚所记者不过如右。此外如更有可检处。随阅辄示宜矣。且不东西不二三之说。疑出于程子只是中只是内之意。而互相校勘。终不符契。或各自一说而意不相照者耶。俱望存想。蔡氏书序云间有经承口授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然其有剩有阙。不可掩也。今添钱乐于耿寿昌之下。自衡长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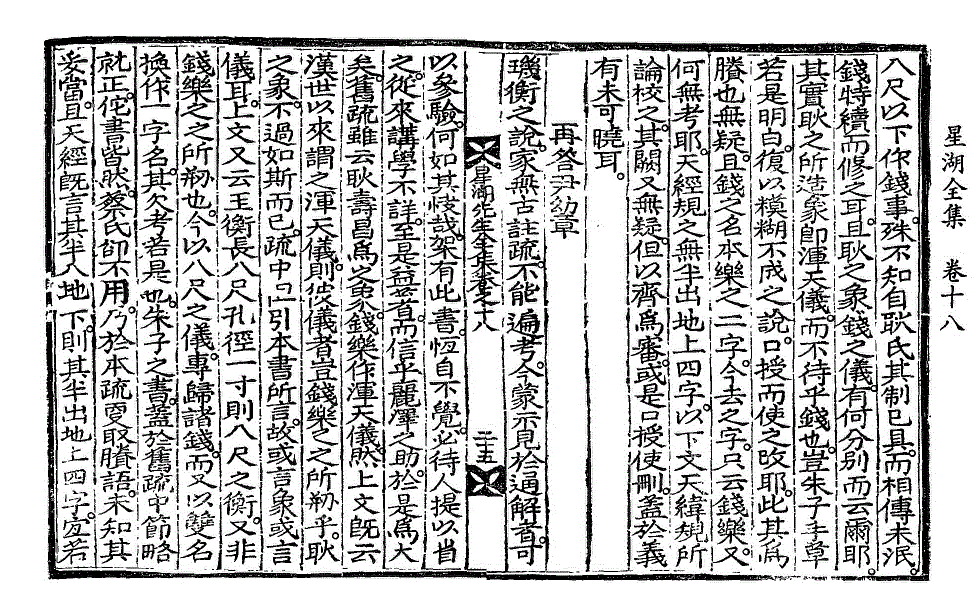 八尺以下作钱事。殊不知自耿氏其制已具。而相传未泯。钱特续而修之耳。且耿之象钱之仪。有何分别而云尔耶。其实耿之所造象即浑天仪。而不待乎钱也。岂朱子手草若是明白。复以模糊不成之说。口授而使之改耶。此其为剩也无疑。且钱之名本乐之二字。今去之字。只云钱乐。又何无考耶。天经规之无半出地上四字。以下文天纬规所论校之。其阙又无疑。但以齐为审。或是口授使删。盖于义有未可晓耳。
八尺以下作钱事。殊不知自耿氏其制已具。而相传未泯。钱特续而修之耳。且耿之象钱之仪。有何分别而云尔耶。其实耿之所造象即浑天仪。而不待乎钱也。岂朱子手草若是明白。复以模糊不成之说。口授而使之改耶。此其为剩也无疑。且钱之名本乐之二字。今去之字。只云钱乐。又何无考耶。天经规之无半出地上四字。以下文天纬规所论校之。其阙又无疑。但以齐为审。或是口授使删。盖于义有未可晓耳。再答尹幼章
玑衡之说。家无古注疏。不能遍考。今蒙示见于通解者。可以参验。何如其快哉。架有此书。恒自不觉。必待人提以省之。从来讲学不详。至是益著。而信乎丽泽之助。于是为大矣。旧疏虽云耿寿昌为之象。钱乐作浑天仪。然上文既云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则彼仪者岂钱乐之之所刱乎。耿之象。不过如斯而已。疏中但引本书所言。故或言象或言仪耳。上文又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则八尺之衡。又非钱乐之之所刱也。今以八尺之仪。专归诸钱。而又以双名换作一字名。其欠考若是也。朱子之书。盖于旧疏中节略就正。佗书皆然。蔡氏却不用。乃于本疏更取剩语。未知其妥当。且天经既言其半入地下。则其半出地上四字。宜若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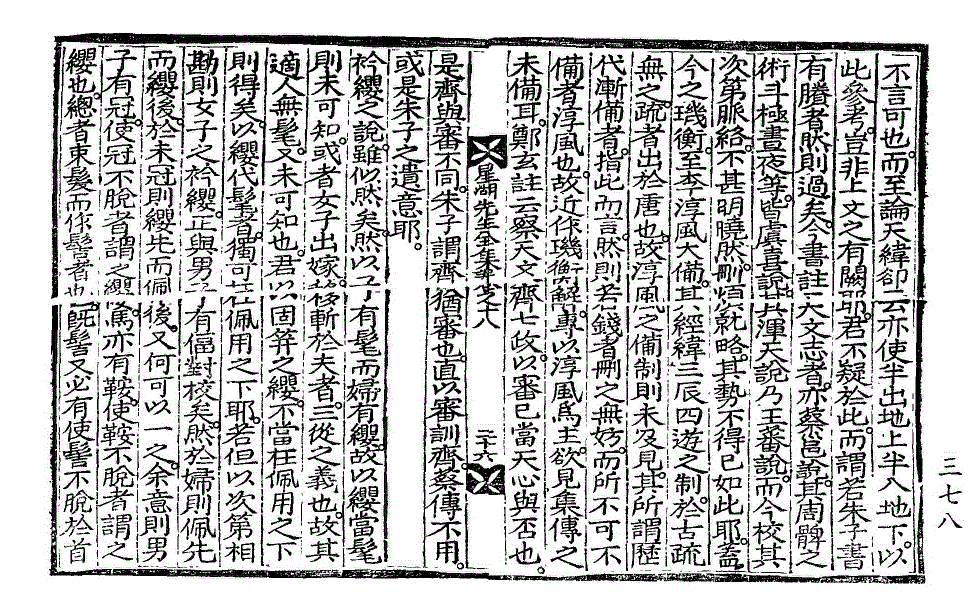 不言可也。而至论天纬却云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以此参考。岂非上文之有阙耶。君不疑于此。而谓若朱子书有剩者然则过矣。今书注天文志者。亦蔡邕说。其周髀之术斗极昼夜等。皆虞喜说。其浑天说乃王蕃说。而今校其次第脉络。不甚明晓然。删烦就略。其势不得已如此耶。盖今之玑衡。至李淳风大备。其经纬三辰四游之制。于古疏无之。疏者出于唐也。故淳风之备制则未及见。其所谓历代渐备者。指此而言。然则若钱者删之无妨。而所不可不备者淳风也。故近作玑衡解。专以淳风为主。欲见集传之未备耳。郑玄注云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也。是齐与审不同。朱子谓齐犹审也。直以审训齐。蔡传不用。或是朱子之遗意耶。
不言可也。而至论天纬却云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以此参考。岂非上文之有阙耶。君不疑于此。而谓若朱子书有剩者然则过矣。今书注天文志者。亦蔡邕说。其周髀之术斗极昼夜等。皆虞喜说。其浑天说乃王蕃说。而今校其次第脉络。不甚明晓然。删烦就略。其势不得已如此耶。盖今之玑衡。至李淳风大备。其经纬三辰四游之制。于古疏无之。疏者出于唐也。故淳风之备制则未及见。其所谓历代渐备者。指此而言。然则若钱者删之无妨。而所不可不备者淳风也。故近作玑衡解。专以淳风为主。欲见集传之未备耳。郑玄注云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也。是齐与审不同。朱子谓齐犹审也。直以审训齐。蔡传不用。或是朱子之遗意耶。衿缨之说。虽似然矣。然以子有髦而妇有缨。故以缨当髦则未可知。或者女子出嫁。移斩于夫者。三从之义也。故其适人无髦。又未可知也。君以固笄之缨。不当在佩用之下则得矣。以缨代髦者。独可在佩用之下耶。若但以次第相勘则女子之衿缨。正与男子有偪对校矣。然于妇则佩先而缨后。于未冠则缨先而佩后。又何可以一之。余意则男子有冠。使冠不脱者谓之缨。马亦有鞍。使鞍不脱者谓之缨也。总者束发而作髻者也。既髻又必有使髻不脱于首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9H 页
 者。如男子之用缨也。故亦欲以缨当之。其用与总不同也。其未冠笄。既总而又角。恐又有缨以固之者。夫笄者固髻者也。虽总而又必待笄而固之。其未笄之有缨。何足疑哉。曲礼所谓许嫁缨者。有笄而缨。此如男子之有冠而缨也。其未冠笄之有缨。虽总角亦非系不固。故比类而称缨。似无不可。若如旧注则秽气触污。独可阙于子事父母耶。
者。如男子之用缨也。故亦欲以缨当之。其用与总不同也。其未冠笄。既总而又角。恐又有缨以固之者。夫笄者固髻者也。虽总而又必待笄而固之。其未笄之有缨。何足疑哉。曲礼所谓许嫁缨者。有笄而缨。此如男子之有冠而缨也。其未冠笄之有缨。虽总角亦非系不固。故比类而称缨。似无不可。若如旧注则秽气触污。独可阙于子事父母耶。士丧注四时祭焉者。欲著大祥前有朔望祭。大祥后始有四时祭。檀弓云以虞易奠。既夕礼云犹朝夕哭不奠。此为不复朝夕奠之證。若朔月荐新之类。虽不言其有无。理当不废矣。若卒哭不复朝夕馈。又祥前不举四时祭。又无朔月荐新。则三年却是都无事也。宁有是耶。卒哭以吉祭易丧祭。此礼易而祭则举也。既虞不复称奠则或者朔月荐新。亦稍有变吉之礼耶。是则容有其义。若将谓古礼无有则决不可。家礼葬前之无缩酒者。体魄未复土。故自虞以下必有缩酒。若朔望者殷奠也。似无报魂而不报魄之理也。卒哭以吉祭易丧祭则虞亦丧祭也。而缩酒报魄则岂可以丧祭之故而阙之耶。更须思之。
答尹幼章(乙巳)
向蒙辱书。苦缘无便。旷不修谢。玆又奉今月八日书。盈把入怀。奚啻百朋。又伏审阳嘘物长。福履佳胜。尤以为慰。瀷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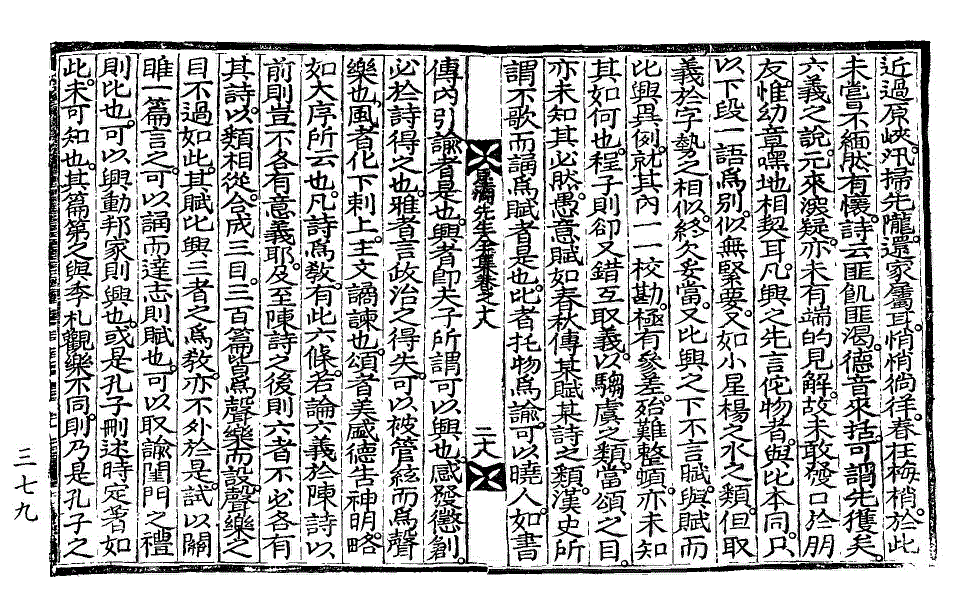 近过原峡。汛扫先陇。还家属耳。悄悄徜徉。春在梅梢。于此未尝不缅然有怀。诗云匪饥匪渴。德音来括。可谓先获矣。六义之说。元来深疑。亦未有端的见解。故未敢发口于朋友。惟幼章嘿地相契耳。凡兴之先言佗物者。与比本同。只以下段一语为别。似无紧要。又如小星杨之水之类。但取义于字势之相似。终欠妥当。又比兴之下不言赋。与赋而比兴异例。就其内一一校勘。极有参差。殆难整顿。亦未知其如何也。程子则却又错互取义。以驺虞之类。当颂之目。亦未知其必然。愚意赋如春秋传某赋某诗之类。汉史所谓不歌而诵为赋者是也。比者托物为谕。可以晓人。如书传内引谕者是也。兴者即夫子所谓可以兴也。感发惩创。必于诗得之也。雅者言政治之得失。可以被管弦而为声乐也。风者化下刺上。主文谲谏也。颂者美盛德告神明。略如大序所云也。凡诗为教。有此六条。若论六义于陈诗以前则岂不各有意义耶。及至陈诗之后则六者不必各有其诗。以类相从。合成三目。三百篇皆为声乐而设。声乐之目不过如此。其赋比兴三者之为教。亦不外于是。试以关睢一篇言之。可以诵而达志则赋也。可以取谕闺门之礼则比也。可以兴动邦家则兴也。或是孔子删述时定著如此。未可知也。其篇第之与季札观乐不同。则乃是孔子之
近过原峡。汛扫先陇。还家属耳。悄悄徜徉。春在梅梢。于此未尝不缅然有怀。诗云匪饥匪渴。德音来括。可谓先获矣。六义之说。元来深疑。亦未有端的见解。故未敢发口于朋友。惟幼章嘿地相契耳。凡兴之先言佗物者。与比本同。只以下段一语为别。似无紧要。又如小星杨之水之类。但取义于字势之相似。终欠妥当。又比兴之下不言赋。与赋而比兴异例。就其内一一校勘。极有参差。殆难整顿。亦未知其如何也。程子则却又错互取义。以驺虞之类。当颂之目。亦未知其必然。愚意赋如春秋传某赋某诗之类。汉史所谓不歌而诵为赋者是也。比者托物为谕。可以晓人。如书传内引谕者是也。兴者即夫子所谓可以兴也。感发惩创。必于诗得之也。雅者言政治之得失。可以被管弦而为声乐也。风者化下刺上。主文谲谏也。颂者美盛德告神明。略如大序所云也。凡诗为教。有此六条。若论六义于陈诗以前则岂不各有意义耶。及至陈诗之后则六者不必各有其诗。以类相从。合成三目。三百篇皆为声乐而设。声乐之目不过如此。其赋比兴三者之为教。亦不外于是。试以关睢一篇言之。可以诵而达志则赋也。可以取谕闺门之礼则比也。可以兴动邦家则兴也。或是孔子删述时定著如此。未可知也。其篇第之与季札观乐不同。则乃是孔子之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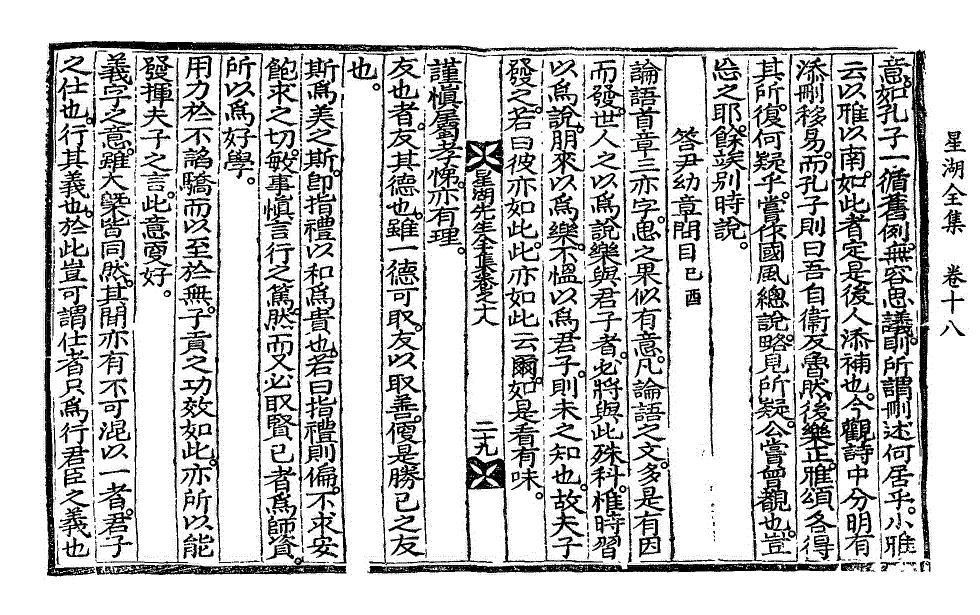 意。如孔子一循旧例。无容思议。则所谓删述何居乎。小雅云以雅以南。如此者定是后人添补也。今观诗中分明有添删移易。而孔子则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复何疑乎。尝作国风总说。略见所疑。公尝曾睹也。岂忘之耶。馀俟别时说。
意。如孔子一循旧例。无容思议。则所谓删述何居乎。小雅云以雅以南。如此者定是后人添补也。今观诗中分明有添删移易。而孔子则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复何疑乎。尝作国风总说。略见所疑。公尝曾睹也。岂忘之耶。馀俟别时说。答尹幼章问目(己酉)
论语首章三亦字。思之果似有意。凡论语之文。多是有因而发。世人之以为说乐与君子者。必将与此殊科。惟时习以为说。朋来以为乐。不愠以为君子。则未之知也。故夫子发之。若曰彼亦如此。此亦如此云尔。如是看有味。
谨慎属孝悌。亦有理。
友也者。友其德也。虽一德可取。友以取善。便是胜己之友也。
斯为美之斯。即指礼以和为贵也。若曰指礼则偏。不求安饱求之切。敏事慎言行之笃。然而又必取贤己者为师资。所以为好学。
用力于不谄骄而以至于无。子贡之功效如此。亦所以能发挥夫子之言。此意更好。
义字之意。虽大槩皆同然。其间亦有不可混以一者。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于此岂可谓仕者只为行君臣之义也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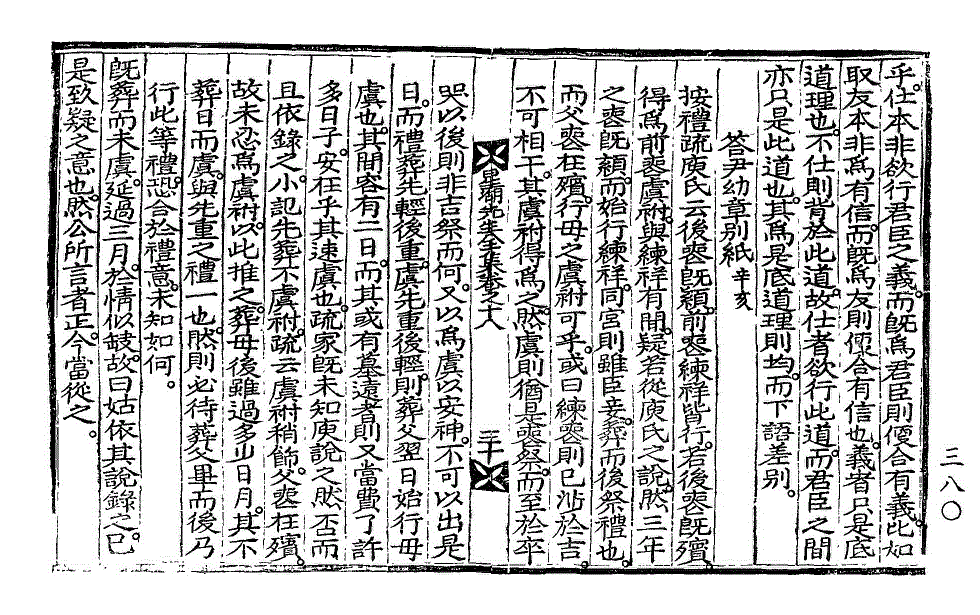 乎。仕本非欲行君臣之义。而既为君臣则便合有义。比如取友本非为有信。而既为友则便合有信也。义者只是底道理也。不仕则背于此道。故仕者欲行此道。而君臣之间亦只是此道也。其为是底道理则均。而下语差别。
乎。仕本非欲行君臣之义。而既为君臣则便合有义。比如取友本非为有信。而既为友则便合有信也。义者只是底道理也。不仕则背于此道。故仕者欲行此道。而君臣之间亦只是此道也。其为是底道理则均。而下语差别。答尹幼章别纸(辛亥)
按礼疏庾氏云后丧既顈。前丧练祥皆行。若后丧既殡。得为前丧虞祔。与练祥有间。疑若从庾氏之说。然三年之丧既顈。而始行练祥。同宫则虽臣妾。葬而后祭礼也。而父丧在殡。行母之虞祔可乎。或曰练丧则已涉于吉。不可相干。其虞祔得为之。然虞则犹是丧祭。而至于卒哭以后则非吉祭而何。又以为虞以安神。不可以出是日。而礼葬先轻后重。虞先重后轻。则葬父翌日始行母虞也。其间容有二日。而其或有墓远者则又当费了许多日子。安在乎其速虞也。疏家既未知庾说之然否而且依录之。小记先葬不虞祔。疏云虞祔稍饰。父丧在殡。故未忍为虞祔。以此推之。葬母后虽过多少日月。其不葬日而虞。与先重之礼一也。然则必待葬父毕而后乃行此等礼。恐合于礼意。未知如何。
既葬而未虞。延过三月。于情似缺。故曰姑依其说录之。已是致疑之意也。然公所言者正。今当从之。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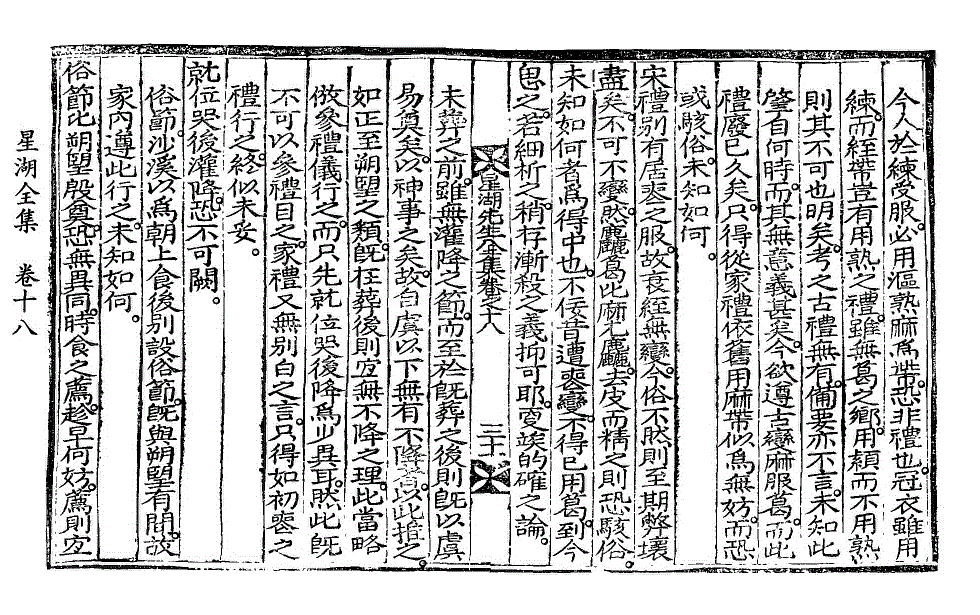 今人于练受服。必用沤熟麻为带。恐非礼也。冠衣虽用练。而绖带岂有用熟之礼。虽无葛之乡。用顈而不用熟则其不可也明矣。考之古礼无有。备要亦不言。未知此肇自何时。而其无意义甚矣。今欲遵古变麻服葛。而此礼废已久矣。只得从家礼依旧用麻带似为无妨。而恐或骇俗。未知如何。
今人于练受服。必用沤熟麻为带。恐非礼也。冠衣虽用练。而绖带岂有用熟之礼。虽无葛之乡。用顈而不用熟则其不可也明矣。考之古礼无有。备要亦不言。未知此肇自何时。而其无意义甚矣。今欲遵古变麻服葛。而此礼废已久矣。只得从家礼依旧用麻带似为无妨。而恐或骇俗。未知如何。宋礼别有居丧之服。故衰绖无变。今俗不然则至期弊坏尽矣。不可不变。然粗葛比麻尤粗。去皮而精之则恐骇俗。未知如何者为得中也。不佞昔遭丧变。不得已用葛。到今思之。若细析之。稍存渐杀之义抑可耶。更俟的确之论。
未葬之前。虽无灌降之节。而至于既葬之后则既以虞易奠矣。以神事之矣。故自虞以下无有不降者。以此推之。如正至朔望之类。既在葬后则宜无不降之理。此当略仿参礼仪行之。而只先就位哭后降为少异耳。然此既不可以参礼目之。家礼又无别白之言。只得如初丧之礼行之。终似未妥。
就位哭后灌降。恐不可阙。
俗节。沙溪以为朝上食后别设俗节。既与朔望有间。故家内遵此行之。未知如何。
俗节比朔望殷奠。恐无异同。时食之荐。趁早何妨。荐则宜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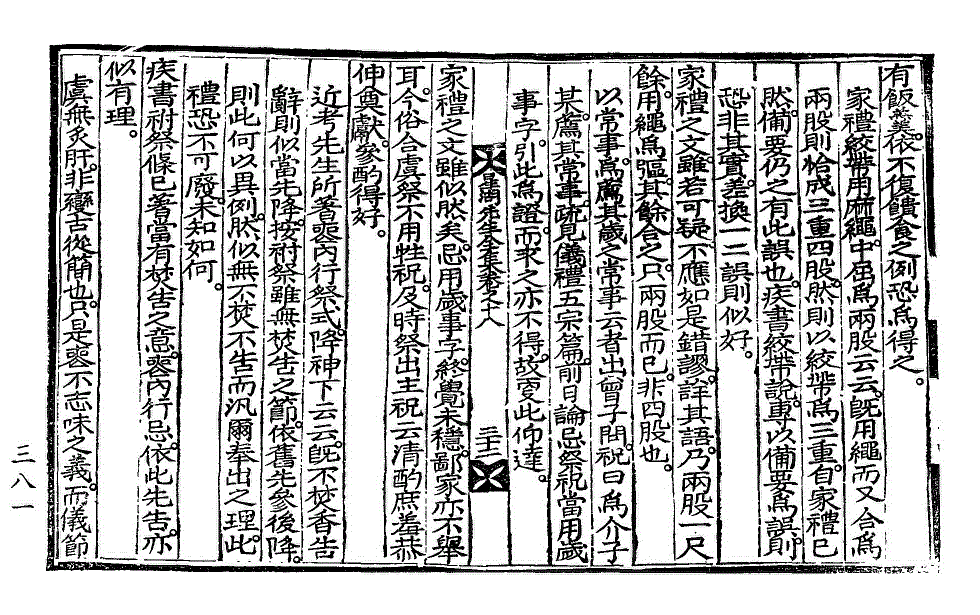 有饭羹。依不复馈食之例恐为得之。
有饭羹。依不复馈食之例恐为得之。家礼绞带用麻绳。中屈为两股云云。既用绳而又合为两股则恰成三重四股。然则以绞带为三重。自家礼已然。备要仍之有此误也。疾书绞带说。专以备要为误。则恐非其实。差换一二误则似好。
家礼之文。虽若可疑。不应如是错谬。详其语。乃两股一尺馀。用绳为彄。其馀合之。只两股而已。非四股也。
以常事。为荐其岁之常事云者出曾子问。祝曰为介子某。荐其常事。疏见仪礼五宗篇。前日论忌祭祝当用岁事字。引此为證。而求之亦不得。故更此仰达。
家礼之文虽似然矣。忌用岁事字。终觉未稳。鄙家亦不举耳。今俗合虞祭不用牲祝。及时祭出主祝云清酌庶羞恭伸奠献。参酌得好。
近考先生所著丧内行祭式。降神下云云。既不焚香告辞则似当先降。按祔祭虽无焚告之节。依旧先参后降。则此何以异例。然似无不焚不告而汎尔奉出之理。此礼恐不可废。未知如何。
疾书祔祭条已著当有焚告之意。丧内行忌。依此先告。亦似有理。
虞无炙肝。非变古从简也。只是丧不志味之义。而仪节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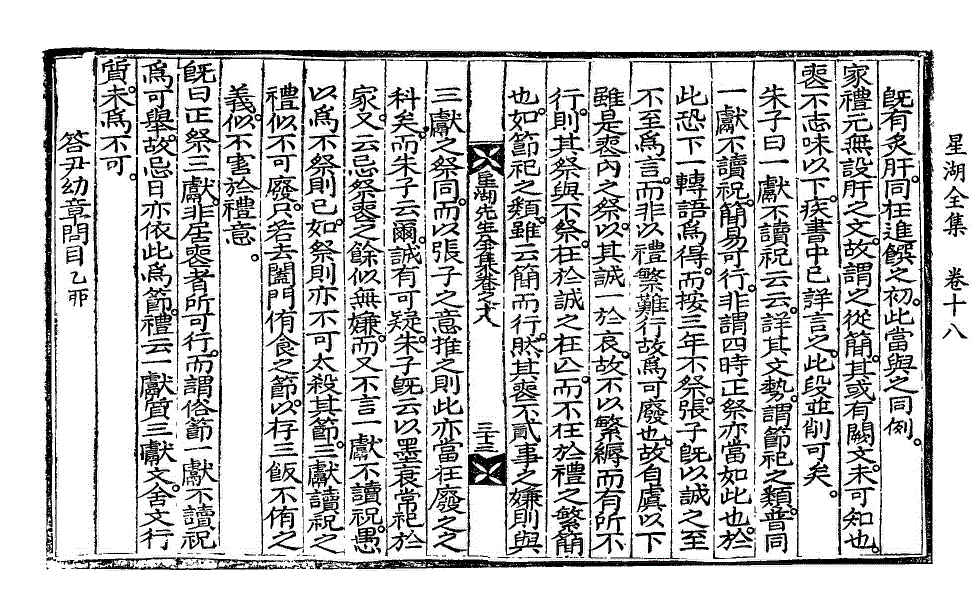 既有炙肝。同在进馔之初。此当与之同例。
既有炙肝。同在进馔之初。此当与之同例。家礼元无设肝之文。故谓之从简。其或有阙文。未可知也。丧不志味以下。疾书中已详言之。此段并削可矣。
朱子曰一献不读祝云云。详其文势。谓节祀之类。普同一献不读祝。简易可行。非谓四时正祭亦当如此也。于此恐下一转语为得。而按三年不祭。张子既以诚之至不至为言。而非以礼繁难行故为可废也。故自虞以下虽是丧内之祭。以其诚一于哀。故不以繁缛而有所不行。则其祭与不祭。在于诚之在亡。而不在于礼之繁简也。如节祀之类。虽云简而行。然其丧不贰事之嫌则与三献之祭同。而以张子之意推之则此亦当在废之之科矣。而朱子云尔。诚有可疑。朱子既云以墨衰常祀于家。又云忌祭丧之馀似无嫌。而又不言一献不读祝。愚以为不祭则已。如祭则亦不可太杀其节。三献读祝之礼似不可废。只若去阖门侑食之节。以存三饭不侑之义。似不害于礼意。
既曰正祭三献。非居丧者所可行。而谓俗节一献不读祝为可举。故忌日亦依此为节。礼云一献质三献文。舍文行质。未为不可。
答尹幼章问目(乙卯)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2L 页
 改葬服制应服缌者外子姓。依丘氏素服布巾。佗人依王肃加麻帽子白带。恐合礼意否。
改葬服制应服缌者外子姓。依丘氏素服布巾。佗人依王肃加麻帽子白带。恐合礼意否。当如来示。而佗人加麻恐骇俗。
备要改葬设奠柩前条。有举哀再拜酹酒再拜。若一依丧奠则似当如朝夕哭之礼。若如常祭则似更辞神再拜。而如是斑驳可乎。按改葬缌郑注其奠如大敛。则如朝夕哭之仪似可矣。未知如何。
当如朝夕哭奠。
按家礼通礼有事则告条。虽不遍告诸位。而亦无奉出所当告之主。而朱子有改葬祭告出主于寝之论。故备要依此只奉所改葬之主而祭之。然告追赠。只告所赠之龛。而有茶酒并设之礼。改葬祭告。恐不可异例。而祭告时依题主后祝斟酒告之例。未知得当否。
依家礼并设茶酒。而只告当告之龛。使服轻者行之。
按郑注改葬者明棺物毁败。改设之如葬时云。则凡玄纁帷㡛之物。自当一如始葬。而又云其奠如大敛。从庙之庙。从墓之墓。礼宜同也。又曰奠如大敛。而从墓之墓与朝庙同。以此推之。礼宜与始丧不同矣。神魂在堂。体魄在山。灵座之设。恐非礼意。而下室之馈。亦不可复行。神非饮食无依。朝夕之奠。似当有之。而灵座上食。恐非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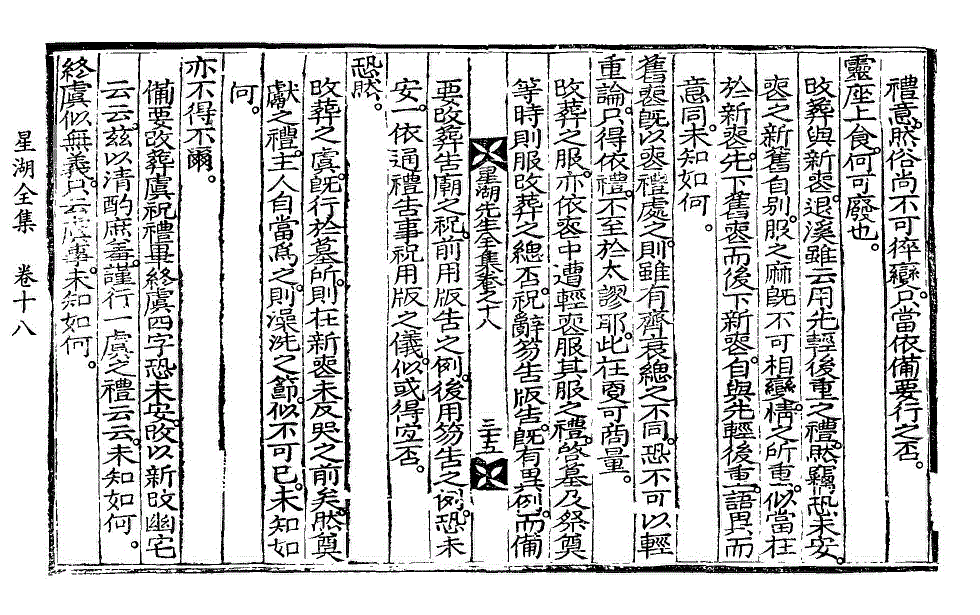 礼意。然俗尚不可猝变。只当依备要行之否。
礼意。然俗尚不可猝变。只当依备要行之否。灵座上食。何可废也。
改葬与新丧。退溪虽云用先轻后重之礼。然窃恐未安。丧之新旧自别。服之麻既不可相变。情之所重。似当在于新丧。先下旧丧而后下新丧。自与先轻后重。语异而意同。未知如何。
旧丧既以丧礼处之。则虽有齐衰缌之不同。恐不可以轻重论。只得依礼。不至于太谬耶。此在更可商量。
改葬之服。亦依丧中遭轻丧服其服之礼。启墓及祭奠等时则服改葬之缌否。祝辞笏告版告。既有异例。而备要改葬告庙之祝。前用版告之例。后用笏告之例。恐未安。一依通礼告事祝用版之仪。似或得宜否。
恐然。
改葬之虞。既行于墓所。则在新丧未反哭之前矣。然奠献之礼。主人自当为之。则澡洗之节。似不可已。未知如何。
亦不得不尔。
备要改葬虞祝礼毕终虞四字恐未安。改以新改幽宅云云。玆以清酌庶羞。谨行一虞之礼云云。未知如何。
终虞似无义。只云虞事。未知如何。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3L 页
 朱子曰葬毕告庙哭。毕事告庙有哭。果合礼意耶。恐似未安。未知如何。
朱子曰葬毕告庙哭。毕事告庙有哭。果合礼意耶。恐似未安。未知如何。告庙哭虽似未安。礼云亲族有丧。必哭庙。今既以丧礼处之。依朱子说。亦或无害耶。
答尹幼章(乙卯)
音便陔隔。方谋因人书候。不意专伻问讯。奉读哀札。虽以为慰。又阅源明书。极以哀衰疾绵缀为忧。丧威荐叠。俨然衰绖。安得不尔。毁不危身。为无后也。况复春前辙可鉴。垂老之年。保性终孝。亦不可不念。忝居朋友之末。向傃忧叹。其可形谕。瀷顷日薄言历吊。未暇少淹。不但悼死。生别亦良苦矣。归道得一绝云世间无事无遗憾。未若身亡学未成。十数年来多少业。一尘吹散果何名。情见于辞。不敢不浼闻耳。瀷孤陋晚闻。绝无师友之益。惟公兄弟是依是赖。自失复春。尤觉伥伥。志铭撰次。用发幽光。固瀷之志也。今观行录。嗟惋尤增。渠平生气像尽好。和静乐易。不露声色。而人便畏惮。瀷每服此一段。今何可复得耶。耳老祭文亦切实可玩。惟以与天地同其悠久者。勉之于身。为后死之责。则幽明之间。灵通相照矣。此公久未相见。顷得书更于四书中亲切下功。向来勤劬易学。颇有不循阶级之虑。从今周道整驾。何地不届。瀷撑过为幸。近又被偷儿所困。衣
星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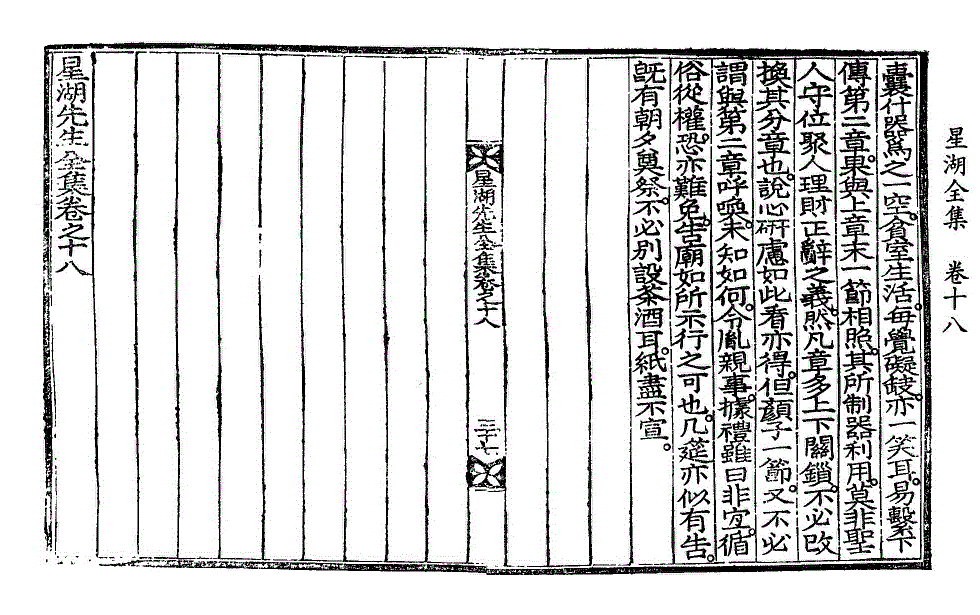 囊什器为之一空。贫室生活。每觉碍缺。亦一笑耳。易系下传第二章。果与上章末一节相照。其所制器利用。莫非圣人守位聚人理财正辞之义。然凡章多上下关锁。不必改换其分章也。说心研虑如此看亦得。但颜子一节。又不必谓与第二章呼唤。未知如何。令胤亲事。据礼虽曰非宜。循俗从权。恐亦难免。告庙如所示行之可也。几筵亦似有告。既有朝夕奠祭。不必别设茶酒耳。纸尽不宣。
囊什器为之一空。贫室生活。每觉碍缺。亦一笑耳。易系下传第二章。果与上章末一节相照。其所制器利用。莫非圣人守位聚人理财正辞之义。然凡章多上下关锁。不必改换其分章也。说心研虑如此看亦得。但颜子一节。又不必谓与第二章呼唤。未知如何。令胤亲事。据礼虽曰非宜。循俗从权。恐亦难免。告庙如所示行之可也。几筵亦似有告。既有朝夕奠祭。不必别设茶酒耳。纸尽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