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x 页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杂录]
[杂录]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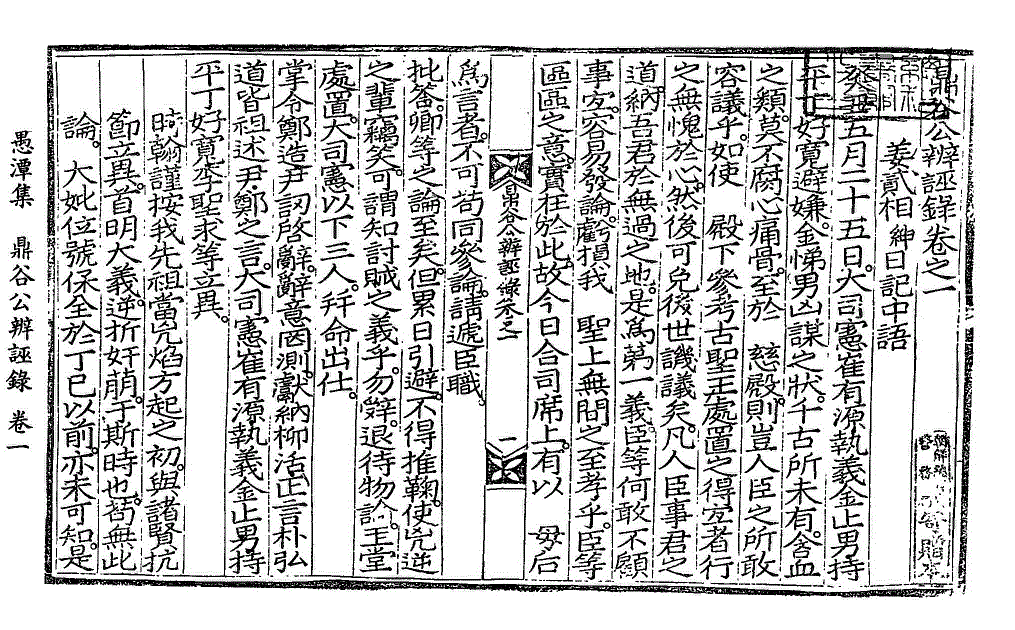 姜贰相(绅)日记中语
姜贰相(绅)日记中语癸丑五月二十五日。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避嫌。金悌男凶谋之状。千古所未有。含血之类。莫不腐心痛骨。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之所敢容议乎。如使 殿下参考古圣王处置之得宜者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免后世讥议矣。凡人臣事君之道。纳吾君于无过之地。是为第一义。臣等何敢不顾事宜。容易发论。亏损我 圣上无间之至孝乎。臣等区区之意。实在于此。故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请递臣职。
批答。卿等之论至矣。但累日引避。不得推鞠。使凶逆之辈窃笑。可谓知讨贼之义乎。勿辞。退待物论。玉堂处置。大司宪以下三人。并命出仕。
掌令郑造,尹讱启辞。辞意罔测。献纳柳活,正言朴弘道皆祖述尹,郑之言。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李圣求等立异。
时翰谨按我先祖当凶焰方起之初。与诸贤抗节立异。首明大义。逆折奸萌。于斯时也。苟无此论。 大妣位号保全于丁巳以前。亦未可知。是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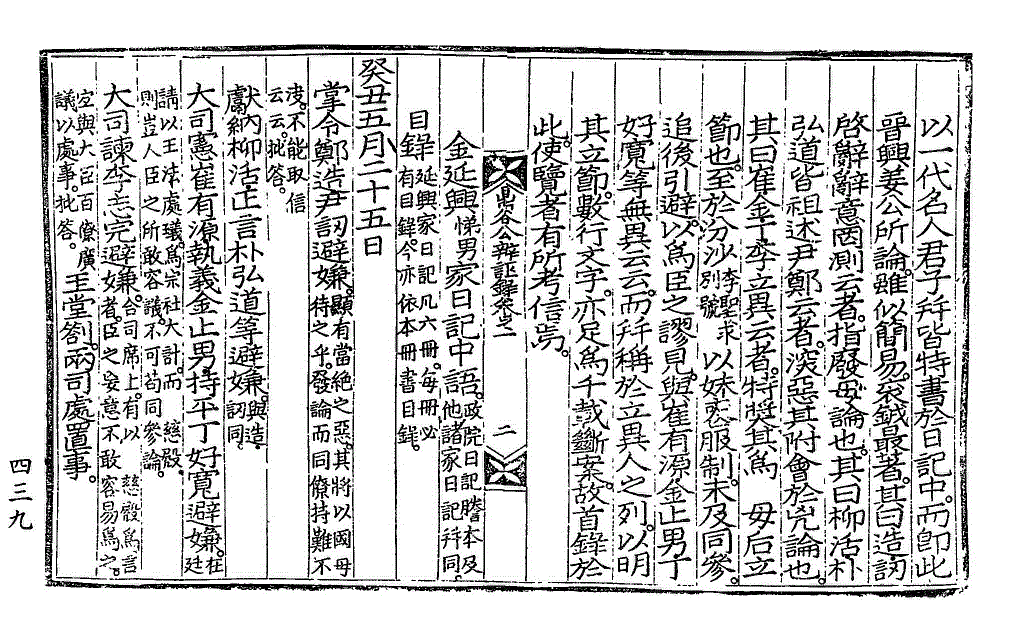 以一代名人君子并皆特书于日记中。而即此晋兴姜公所论。虽似简易。衮钺最著。其曰造,讱启辞辞意罔测云者。指废母论也。其曰柳活,朴弘道皆祖述尹郑云者。深恶其附会于凶论也。其曰崔,金,丁,李立异云者。特奖其为 母后立节也。至于汾沙(李圣求别号)以妹丧服制。未及同参。追后引避。以为臣之谬见。与崔有源,金止男,丁好宽等无异云云。而并称于立异人之列。以明其立节。数行文字。亦足为千载断案。故首录于此。使览者有所考信焉。
以一代名人君子并皆特书于日记中。而即此晋兴姜公所论。虽似简易。衮钺最著。其曰造,讱启辞辞意罔测云者。指废母论也。其曰柳活,朴弘道皆祖述尹郑云者。深恶其附会于凶论也。其曰崔,金,丁,李立异云者。特奖其为 母后立节也。至于汾沙(李圣求别号)以妹丧服制。未及同参。追后引避。以为臣之谬见。与崔有源,金止男,丁好宽等无异云云。而并称于立异人之列。以明其立节。数行文字。亦足为千载断案。故首录于此。使览者有所考信焉。金延兴(悌男)家日记中语。(政院日记誊本及他诸家日记并同。)
目录(延兴家日记凡六册。每册必有目录。今亦依本册书目录。)
癸丑五月二十五日
掌令郑造,尹讱避嫌。(显有当绝之恶。其将以国母待之乎。发论而同僚持难不决。不能取信云云。批答。)
献纳柳活,正言朴弘道等避嫌。(与造,讱同。)
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避嫌。(在廷请以王法处㼁。为宗社大计。而 慈殿,则岂人臣之所敢容议。不可苟同参论。)
大司谏李志完避嫌。(合司席上。有以 慈殿为言者。臣之妄意不敢容易为之。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事。批答。)玉堂劄。两司处置事。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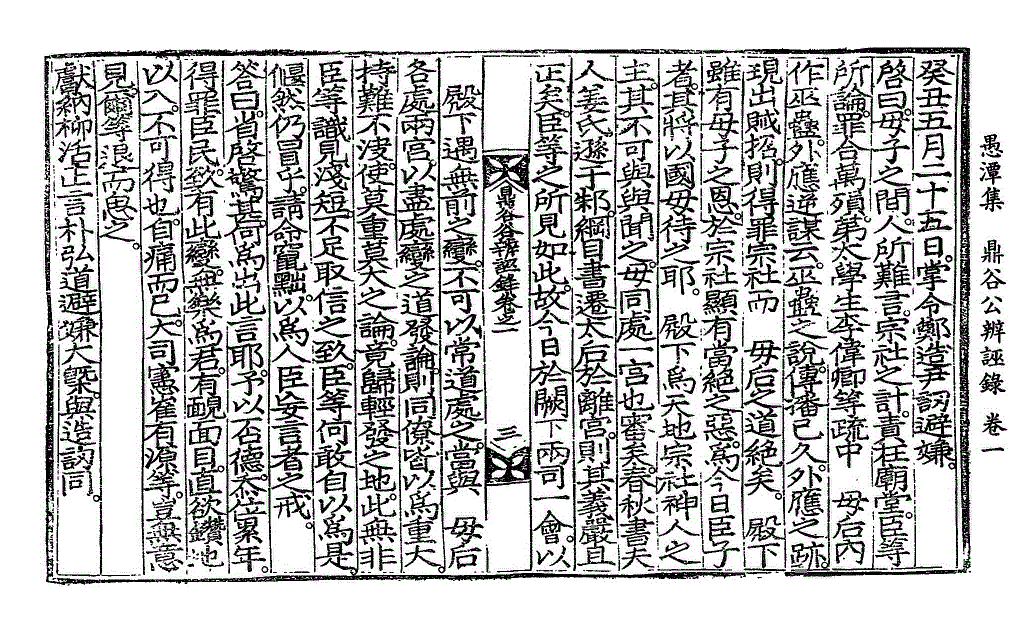 癸丑五月二十五日。掌令郑造,尹讱避嫌。
癸丑五月二十五日。掌令郑造,尹讱避嫌。启曰。母子之间。人所难言。宗社之计。责在庙堂。臣等所论。罪合万殒。第太学生李伟卿等疏中 母后内作巫蛊。外应逆谋云。巫蛊之说。传播已久。外应之迹。现出贼招。则得罪宗社而 母后之道绝矣。 殿下虽有母子之恩。于宗社显有当绝之恶。为今日臣子者。其将以国母待之耶。殿下为天地宗社神人之主。其不可与与闻之。毋同处一宫也审矣。春秋书夫人姜氏逊于邾。纲目书迁太后于离宫。则其义严且正矣。臣等之所见如此。故今日于阙下两司一会。以 殿下遇无前之变。不可以常道处之。当与 母后各处两宫。以尽处变之道发论。则同僚皆以为重大。持难不决。使莫重莫大之论。竟归轻发之地。此无非臣等识见浅短。不足取信之致。臣等何敢自以为是。偃然仍冒乎。请命窜黜。以为人臣妄言者之戒。
答曰。省启惊甚。何为出此言耶。予以否德。忝位累年。得罪臣民。致有此变。无乐为君。有腼面目。直欲钻地以入。不可得也。自痛而已。大司宪崔有源等。岂无意见。尔等退而思之。
献纳柳活,正言朴弘道避嫌大槩。与造,讱同。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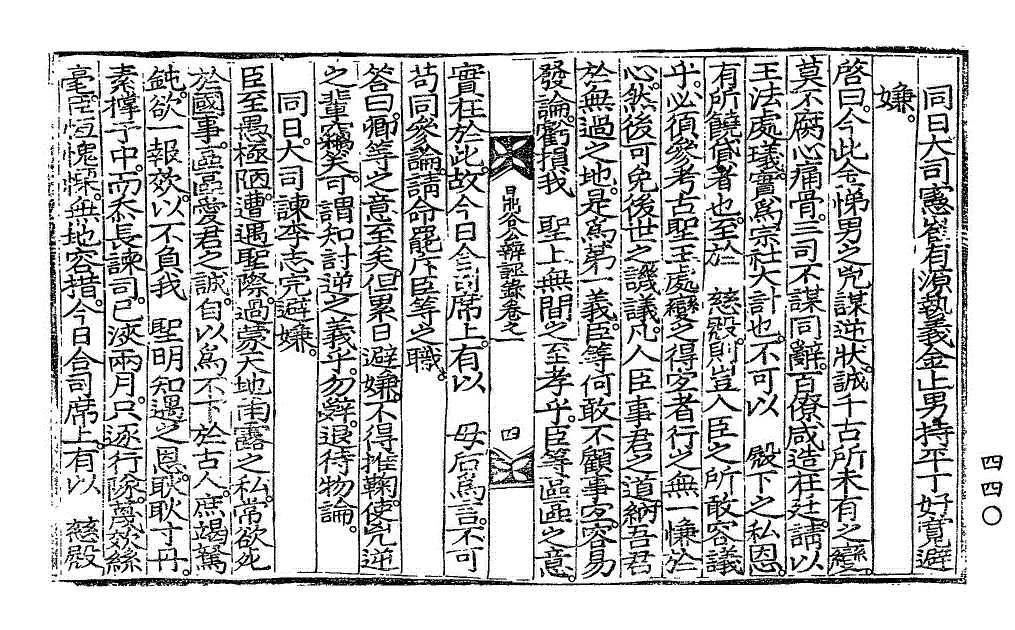 同日。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避嫌。
同日。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避嫌。启曰。今此金悌男之凶谋逆状。诚千古所未有之变。莫不腐心痛骨。三司不谋同辞。百僚咸造在廷。请以王法处㼁。实为宗社大计也。不可以 殿下之私恩。有所饶贷者也。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之所敢容议乎。必须参考古圣王处变之得宜者行之无一慊于心。然后可免后世之讥议。凡人臣事君之道。纳吾君于无过之地。是为第一义。臣等何敢不顾事宜。容易发论。亏损我 圣上无间之至孝乎。臣等区区之意。实在于此。故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不可苟同参论。请命罢斥臣等之职。
答曰。卿等之意至矣。但累日避嫌。不得推鞠。使凶逆之辈窃笑。可谓知讨逆之义乎。勿辞。退待物论。
同日。大司谏李志完避嫌。
臣至愚极陋。遭遇圣际。过蒙天地雨露之私。常欲死于国事。区区爱君之诚。自以为不下于古人。庶竭驽钝。欲一报效。以不负我 圣明知遇之恩。耿耿寸丹。素撑于中。而忝长谏司。已浃两月。只逐行队。蔑效丝毫。臣恒愧慄。无地容措。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慈殿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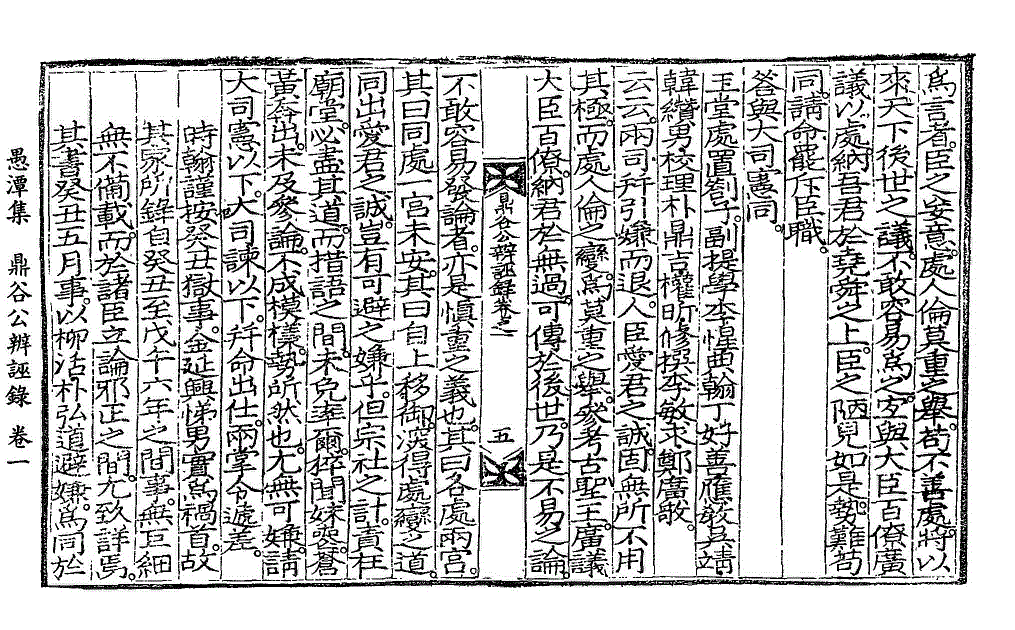 为言者。臣之妄意。处人伦莫重之举。苟不善处。将以来天下后世之议。不敢容易为之。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纳吾君于尧舜之上。臣之陋见如是。势难苟同。请命罢斥臣职。
为言者。臣之妄意。处人伦莫重之举。苟不善处。将以来天下后世之议。不敢容易为之。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纳吾君于尧舜之上。臣之陋见如是。势难苟同。请命罢斥臣职。答与大司宪同。
玉堂处置劄子。副提学李惺,典翰丁好善,应教吴靖,韩缵男,校理朴鼎吉,权昕,修撰李敏求,郑广敬。
云云。两司并引嫌而退。人臣爱君之诚。固无所不用其极。而处人伦之变。为莫重之举。参考古圣王。广议大臣百僚。纳君于无过。可传于后世。乃是不易之论。不敢容易发论者。亦是慎重之义也。其曰各处两宫。其曰同处一宫未安。其曰自上移御。深得处变之道。同出爱君之诚。岂有可避之嫌乎。但宗社之计。责在庙堂。必尽其道。而措语之间。未免率尔。猝闻妹丧。苍黄奔出。未及参论。不成模样。势所然也。尤无可嫌。请大司宪以下。大司谏以下。并命出仕。两掌令递差。
时翰谨按癸丑狱事。金延兴悌男实为祸首。故其家所录自癸丑至戊午六年之间事。无巨细无不备载。而于诸臣立论邪正之间。尤致详焉。其书癸丑五月事。以柳活,朴弘道避嫌。为同于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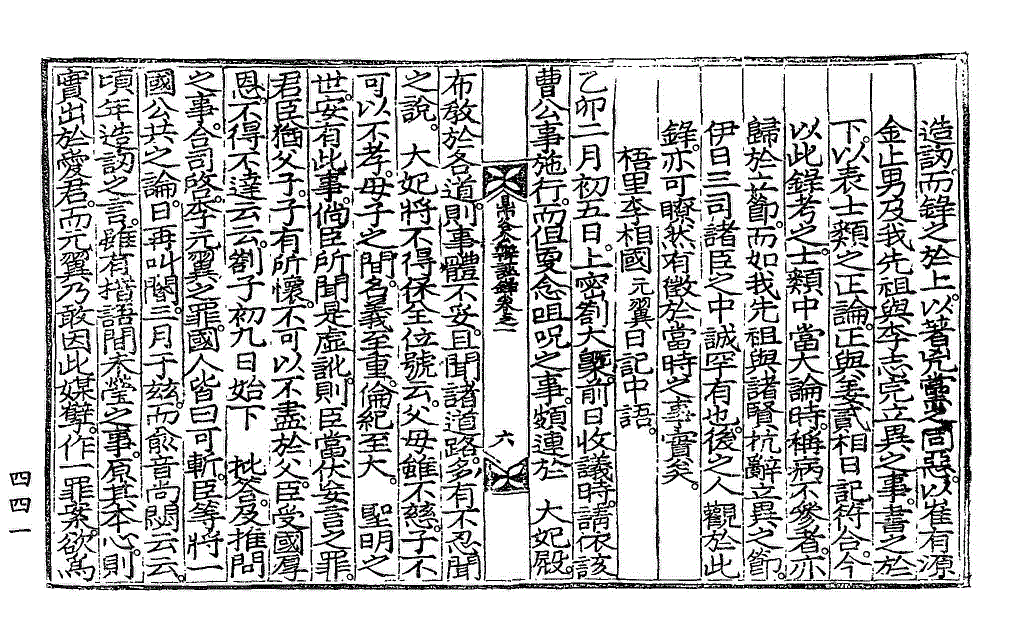 造,讱。而录之于上。以著凶党之同恶。以崔有源,金止男及我先祖与李志完立异之事。书之于下。以表士类之正论。正与姜贰相日记符合。今以此录考之。士类中当大论时。称病不参者。亦归于立节。而如我先祖与诸贤抗辞立异之节。伊日三司诸臣之中诚罕有也。后之人观于此录。亦可瞭然有徵于当时之事实矣。
造,讱。而录之于上。以著凶党之同恶。以崔有源,金止男及我先祖与李志完立异之事。书之于下。以表士类之正论。正与姜贰相日记符合。今以此录考之。士类中当大论时。称病不参者。亦归于立节。而如我先祖与诸贤抗辞立异之节。伊日三司诸臣之中诚罕有也。后之人观于此录。亦可瞭然有徵于当时之事实矣。梧里李相国(元翼)日记中语。
乙卯二月初五日。上密劄大槩。前日收议时。请依该曹公事施行。而但更念咀咒之事。颇连于 大妃殿。布教于各道。则事体不妥。且闻诸道路。多有不忍闻之说。 大妃将不得保全位号云。父母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子之间。名义至重。伦纪至大。 圣明之世。安有此事。倘臣所闻是虚讹。则臣当伏妄言之罪。君臣犹父子。子有所怀。不可以不尽于父。臣受国厚恩。不得不达云云。劄子初九日始下 批答。及推问之事。合司启。李元翼之罪。国人皆曰可斩。臣等将一国公共之论。日再叫阍。三月于玆。而俞音尚閟云云。顷年造,讱之言。虽有措语间未莹之事。原其本心。则实出于爱君。而元翼乃敢因此媒孽。作一罪案。欲为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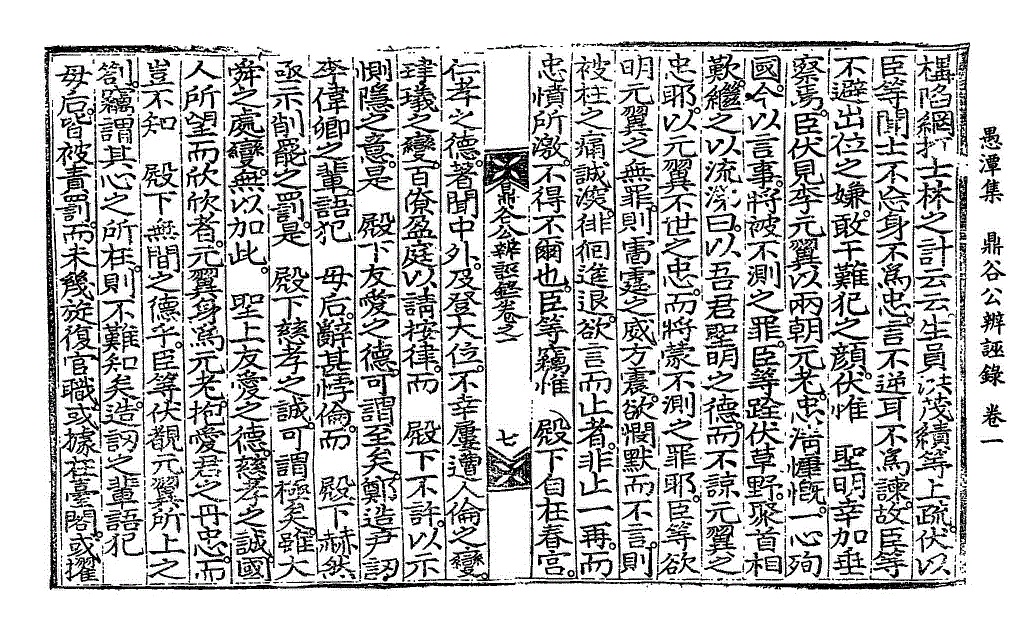 构陷网打士林之计云云。生员洪茂绩等上疏。伏以臣等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等不避出位之嫌。敢干难犯之颜。伏惟 圣明幸加垂察焉。臣伏见李元翼以两朝元老。忠清慷慨。一心殉国。今以言事。将被不测之罪。臣等跧伏草野。聚首相叹。继之以流涕曰。以吾君圣明之德。而不谅元翼之忠耶。以元翼不世之忠。而将蒙不测之罪耶。臣等欲明元翼之无罪。则雷霆之威方震。欲悯默而不言。则被枉之痛诚深。徘徊进退。欲言而止者。非止一再。而忠愤所激。不得不尔也。臣等窃惟 殿下自在春宫。仁孝之德。著闻中外。及登大位。不幸屡遭人伦之变。珒,㼁之变。百僚盈庭以请按律。而 殿下不许。以示恻隐之意。是 殿下友爱之德。可谓至矣。郑造,尹讱,李伟卿之辈。语犯 母后。辞甚悖伦。而 殿下赫然亟示削罢之罚。是 殿下慈孝之诚。可谓极矣。虽大舜之处变。无以加此。 圣上友爱之德。慈孝之诚。国人所望而欣欣者。元翼身为元老。抱爱君之丹忠。而岂不知 殿下无间之德乎。臣等伏睹元翼所上之劄。窃谓其心之所在。则不难知矣。造,讱之辈语犯 母后。皆被责罚。而未几旋复官职。或据在台阁。或擢
构陷网打士林之计云云。生员洪茂绩等上疏。伏以臣等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等不避出位之嫌。敢干难犯之颜。伏惟 圣明幸加垂察焉。臣伏见李元翼以两朝元老。忠清慷慨。一心殉国。今以言事。将被不测之罪。臣等跧伏草野。聚首相叹。继之以流涕曰。以吾君圣明之德。而不谅元翼之忠耶。以元翼不世之忠。而将蒙不测之罪耶。臣等欲明元翼之无罪。则雷霆之威方震。欲悯默而不言。则被枉之痛诚深。徘徊进退。欲言而止者。非止一再。而忠愤所激。不得不尔也。臣等窃惟 殿下自在春宫。仁孝之德。著闻中外。及登大位。不幸屡遭人伦之变。珒,㼁之变。百僚盈庭以请按律。而 殿下不许。以示恻隐之意。是 殿下友爱之德。可谓至矣。郑造,尹讱,李伟卿之辈。语犯 母后。辞甚悖伦。而 殿下赫然亟示削罢之罚。是 殿下慈孝之诚。可谓极矣。虽大舜之处变。无以加此。 圣上友爱之德。慈孝之诚。国人所望而欣欣者。元翼身为元老。抱爱君之丹忠。而岂不知 殿下无间之德乎。臣等伏睹元翼所上之劄。窃谓其心之所在。则不难知矣。造,讱之辈语犯 母后。皆被责罚。而未几旋复官职。或据在台阁。或擢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2L 页
 在清要。人心因此汹扰。道路藉藉。元翼既知人心之如此。又闻人言之如此。岂可如越视秦瘠而不思其有怀必达之义乎。元翼之意必曰以吾君之诚孝而有是事耶。以吾君之处变而有是言耶。吾岂敢诿诸道路之闻而不告吾君耶。至以道路之闻。密封章劄。此实大臣先事入告之义。昔宋英宗皇帝谓其臣韩琦曰。太后待我无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小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馀皆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未闻当时以此罪琦。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况我 殿下以大舜之孝。无英宗之失。元翼岂不知 殿下之诚孝。而谓 殿下有是心有是事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李元翼之心。不可诬也。其劄辞曰。圣人人伦之至。圣明之世。安有此事。是则元翼固信 殿下之诚孝而疑道路之疑者也。呜呼。元翼平生爱君忧国之诚。 圣明之所洞烛。国人之所共知。乃于入地之年。犹不忘君。言不知裁。触犯 天威。惟其所恃者 圣明。所仗者忠信。所爱者君父。所忧者国事也。原其本心。岂有他肠。臣等伏见李伟卿等疏曰。母道已自绝矣。造,讱之辞曰。其可以
在清要。人心因此汹扰。道路藉藉。元翼既知人心之如此。又闻人言之如此。岂可如越视秦瘠而不思其有怀必达之义乎。元翼之意必曰以吾君之诚孝而有是事耶。以吾君之处变而有是言耶。吾岂敢诿诸道路之闻而不告吾君耶。至以道路之闻。密封章劄。此实大臣先事入告之义。昔宋英宗皇帝谓其臣韩琦曰。太后待我无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小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馀皆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未闻当时以此罪琦。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况我 殿下以大舜之孝。无英宗之失。元翼岂不知 殿下之诚孝。而谓 殿下有是心有是事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李元翼之心。不可诬也。其劄辞曰。圣人人伦之至。圣明之世。安有此事。是则元翼固信 殿下之诚孝而疑道路之疑者也。呜呼。元翼平生爱君忧国之诚。 圣明之所洞烛。国人之所共知。乃于入地之年。犹不忘君。言不知裁。触犯 天威。惟其所恃者 圣明。所仗者忠信。所爱者君父。所忧者国事也。原其本心。岂有他肠。臣等伏见李伟卿等疏曰。母道已自绝矣。造,讱之辞曰。其可以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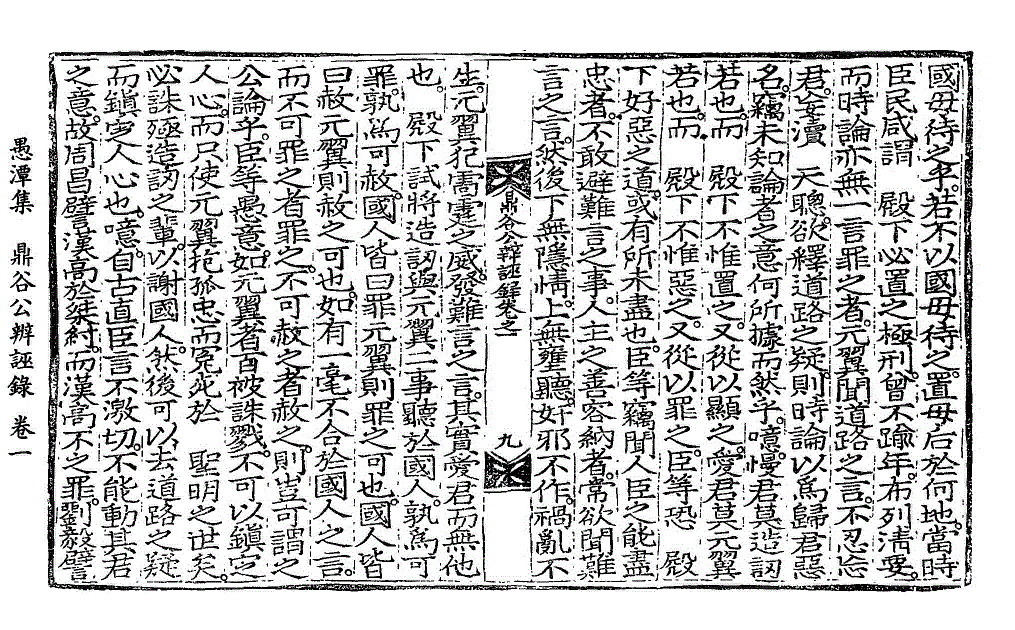 国母待之乎。若不以国母待之。置母后于何地。当时臣民咸谓 殿下必置之极刑。曾不踰年。布列清要。而时论亦无一言罪之者。元翼闻道路之言不忍忘君。妄渎 天聪。欲释道路之疑。则时论以为归君恶名。窃未知论者之意何所据而然乎。噫。慢君莫造,讱若也。而 殿下不惟置之。又从以显之。爱君莫元翼若也。而 殿下不惟恶之。又从以罪之。臣等恐 殿下好恶之道。或有所未尽也。臣等窃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容纳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邪不作。祸乱不生。元翼犯雷霆之威。发难言之言。其实爱君而无他也。 殿下试将造,讱,与元翼二事听于国人。孰为可罪。孰为可赦。国人皆曰罪元翼则罪之可也。国人皆曰赦元翼则赦之可也。如有一毫不合于国人之言。而不可罪之者罪之。不可赦之者赦之。则岂可谓之公论乎。臣等愚意。如元翼者百被诛戮。不可以镇定人心。而只使元翼抱孤忠而冤死于 圣明之世矣。必诛殛造,讱之辈。以谢国人。然后可以去道路之疑而镇定人心也。噫。自古直臣言不激切。不能动其君之意。故周昌譬汉高于桀纣。而汉高不之罪。刘毅譬
国母待之乎。若不以国母待之。置母后于何地。当时臣民咸谓 殿下必置之极刑。曾不踰年。布列清要。而时论亦无一言罪之者。元翼闻道路之言不忍忘君。妄渎 天聪。欲释道路之疑。则时论以为归君恶名。窃未知论者之意何所据而然乎。噫。慢君莫造,讱若也。而 殿下不惟置之。又从以显之。爱君莫元翼若也。而 殿下不惟恶之。又从以罪之。臣等恐 殿下好恶之道。或有所未尽也。臣等窃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容纳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邪不作。祸乱不生。元翼犯雷霆之威。发难言之言。其实爱君而无他也。 殿下试将造,讱,与元翼二事听于国人。孰为可罪。孰为可赦。国人皆曰罪元翼则罪之可也。国人皆曰赦元翼则赦之可也。如有一毫不合于国人之言。而不可罪之者罪之。不可赦之者赦之。则岂可谓之公论乎。臣等愚意。如元翼者百被诛戮。不可以镇定人心。而只使元翼抱孤忠而冤死于 圣明之世矣。必诛殛造,讱之辈。以谢国人。然后可以去道路之疑而镇定人心也。噫。自古直臣言不激切。不能动其君之意。故周昌譬汉高于桀纣。而汉高不之罪。刘毅譬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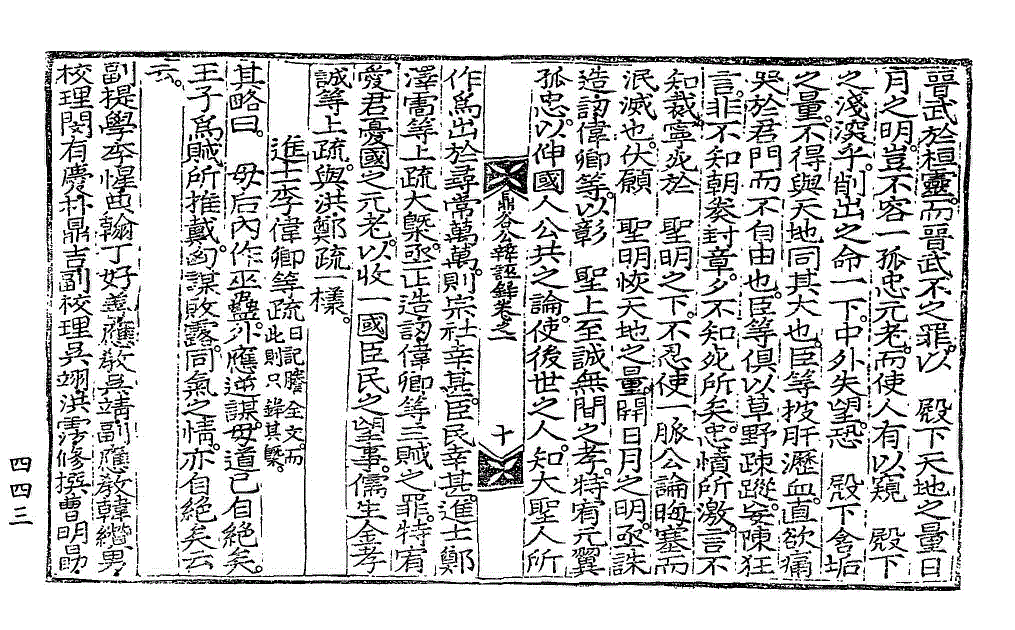 晋武于桓灵。而晋武不之罪。以 殿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岂不容一孤忠元老。而使人有以窥 殿下之浅深乎。削出之命一下。中外失望。恐 殿下含垢之量。不得与天地同其大也。臣等披肝沥血。直欲痛哭于君门而不自由也。臣等俱以草野疏踪。妄陈狂言。非不知朝奏封章。夕不知死所矣。忠愤所激。言不知裁。宁死于 圣明之下。不忍使一脉公论晦塞而泯灭也。伏愿 圣明恢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亟诛造,讱,伟卿等。以彰 圣上至诚无间之孝。特宥元翼孤忠。以伸国人公共之论。使后世之人。知大圣人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则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进士郑泽雷等上疏大槩。亟正造,讱,伟卿等三贼之罪。特宥爱君忧国之元老。以收一国臣民之望事。儒生金孝诚等上疏。与洪,郑疏一样。
晋武于桓灵。而晋武不之罪。以 殿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岂不容一孤忠元老。而使人有以窥 殿下之浅深乎。削出之命一下。中外失望。恐 殿下含垢之量。不得与天地同其大也。臣等披肝沥血。直欲痛哭于君门而不自由也。臣等俱以草野疏踪。妄陈狂言。非不知朝奏封章。夕不知死所矣。忠愤所激。言不知裁。宁死于 圣明之下。不忍使一脉公论晦塞而泯灭也。伏愿 圣明恢天地之量。开日月之明。亟诛造,讱,伟卿等。以彰 圣上至诚无间之孝。特宥元翼孤忠。以伸国人公共之论。使后世之人。知大圣人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则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进士郑泽雷等上疏大槩。亟正造,讱,伟卿等三贼之罪。特宥爱君忧国之元老。以收一国臣民之望事。儒生金孝诚等上疏。与洪,郑疏一样。进士李伟卿等疏(日记誊全文。而此则只录其槩。)
其略曰。 母后内作巫蛊。外应逆谋。母道已自绝矣。王子为贼所推戴。匈谋败露。同气之情。亦自绝矣云云。
副提学李惺,典翰丁好善,应教吴靖,副应教韩缵男,校理闵有庆,朴鼎吉,副校理吴翊,洪霶,修撰曹明勖,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4H 页
 郑广敬等处置劄子。大司谏李志完以臣至愚云云。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慈殿为言者。臣之妄意。处人伦之大变。此实莫重之举。苟不善处。将以来天下后世之议。不可容易为之。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纳吾君于尧舜之上。臣等之谬见如是。不可苟同。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以今此金悌男之凶谋逆状。诚千古所未有。含血之类。莫不腐心痛骨。三司不谋同辞。百僚咸造在廷。请以王法处㼁。实为宗社大计也。不可以 殿下之私恩有所饶贷者也。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所敢议乎。必须参考古圣王处变之得宜者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免后世之讥议。凡人臣事君之道。纳君于无过之地。是为第一义。臣等何敢不顾事宜。容易发论。亏损我 圣上无间之至孝乎。臣等区区之意实在于此。故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掌令郑造,尹讱以母子之间云云。司谏崔东式以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如此莫重之事。岂敢容易为之云云。献纳柳活以国家不幸。变生于至亲。而 母后与闻之说。既出于儒疏。在言责者。固不敢终默。故有此今日之议。而以 圣上至孝之心。其为处变之
郑广敬等处置劄子。大司谏李志完以臣至愚云云。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慈殿为言者。臣之妄意。处人伦之大变。此实莫重之举。苟不善处。将以来天下后世之议。不可容易为之。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纳吾君于尧舜之上。臣等之谬见如是。不可苟同。大司宪崔有源,执义金止男,持平丁好宽以今此金悌男之凶谋逆状。诚千古所未有。含血之类。莫不腐心痛骨。三司不谋同辞。百僚咸造在廷。请以王法处㼁。实为宗社大计也。不可以 殿下之私恩有所饶贷者也。至于 慈殿。则岂人臣所敢议乎。必须参考古圣王处变之得宜者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免后世之讥议。凡人臣事君之道。纳君于无过之地。是为第一义。臣等何敢不顾事宜。容易发论。亏损我 圣上无间之至孝乎。臣等区区之意实在于此。故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掌令郑造,尹讱以母子之间云云。司谏崔东式以今日合司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如此莫重之事。岂敢容易为之云云。献纳柳活以国家不幸。变生于至亲。而 母后与闻之说。既出于儒疏。在言责者。固不敢终默。故有此今日之议。而以 圣上至孝之心。其为处变之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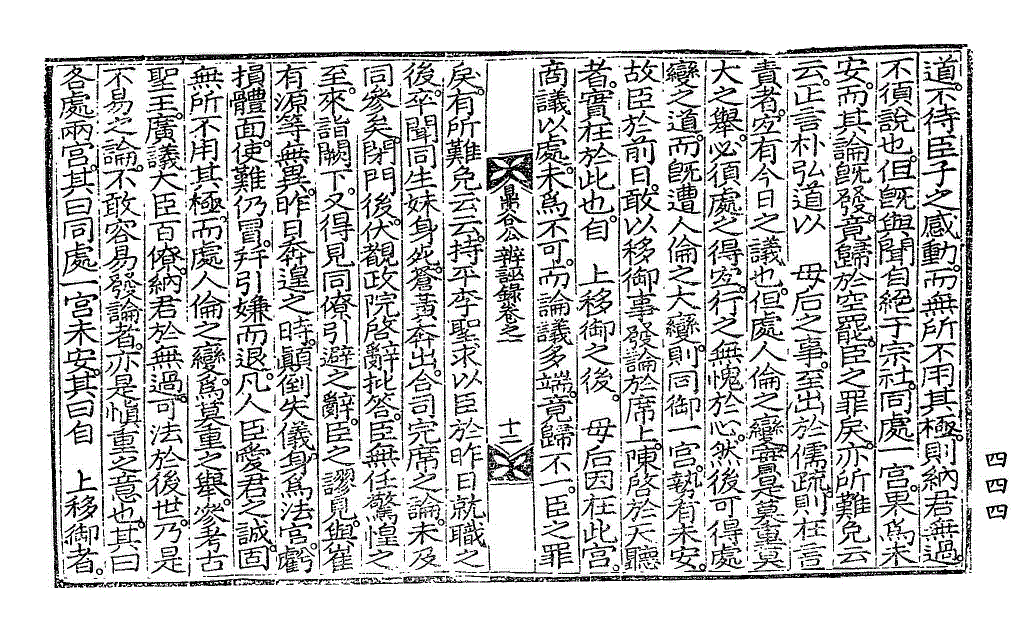 道。不待臣子之感动。而无所不用其极。则纳君无过。不须说也。但既与闻自绝于宗社。同处一宫。果为未安。而其论既发。竟归于空罢。臣之罪戾。亦所难免云云。正言朴弘道以 母后之事。至出于儒疏。则在言责者。宜有今日之议也。但处人伦之变。实是莫重莫大之举。必须处之得宜。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得处变之道。而既遭人伦之大变。则同御一宫。势有未安。故臣于前日。敢以移御事发论于席上。陈启于天听者。实在于此也。自 上移御之后。 母后因在此宫。商议以处。未为不可。而论议多端。竟归不一。臣之罪戾。有所难免云云。持平李圣求以臣于昨日就职之后。卒闻同生妹身死。苍黄奔出。合司完席之论。未及同参矣。闭门后。伏睹政院启辞批答。臣无任惊惶之至。来诣阙下。又得见同僚引避之辞。臣之谬见。与崔有源等无异。昨日奔遑之时。颠倒失仪。身为法官。亏损体面。使难仍冒。并引嫌而退。凡人臣爱君之诚。固无所不用其极。而处人伦之变。为莫重之举。参考古圣王。广议大臣百僚。纳君于无过。可法于后世。乃是不易之论。不敢容易发论者。亦是慎重之意也。其曰各处两宫。其曰同处一宫未安。其曰自 上移御者。
道。不待臣子之感动。而无所不用其极。则纳君无过。不须说也。但既与闻自绝于宗社。同处一宫。果为未安。而其论既发。竟归于空罢。臣之罪戾。亦所难免云云。正言朴弘道以 母后之事。至出于儒疏。则在言责者。宜有今日之议也。但处人伦之变。实是莫重莫大之举。必须处之得宜。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得处变之道。而既遭人伦之大变。则同御一宫。势有未安。故臣于前日。敢以移御事发论于席上。陈启于天听者。实在于此也。自 上移御之后。 母后因在此宫。商议以处。未为不可。而论议多端。竟归不一。臣之罪戾。有所难免云云。持平李圣求以臣于昨日就职之后。卒闻同生妹身死。苍黄奔出。合司完席之论。未及同参矣。闭门后。伏睹政院启辞批答。臣无任惊惶之至。来诣阙下。又得见同僚引避之辞。臣之谬见。与崔有源等无异。昨日奔遑之时。颠倒失仪。身为法官。亏损体面。使难仍冒。并引嫌而退。凡人臣爱君之诚。固无所不用其极。而处人伦之变。为莫重之举。参考古圣王。广议大臣百僚。纳君于无过。可法于后世。乃是不易之论。不敢容易发论者。亦是慎重之意也。其曰各处两宫。其曰同处一宫未安。其曰自 上移御者。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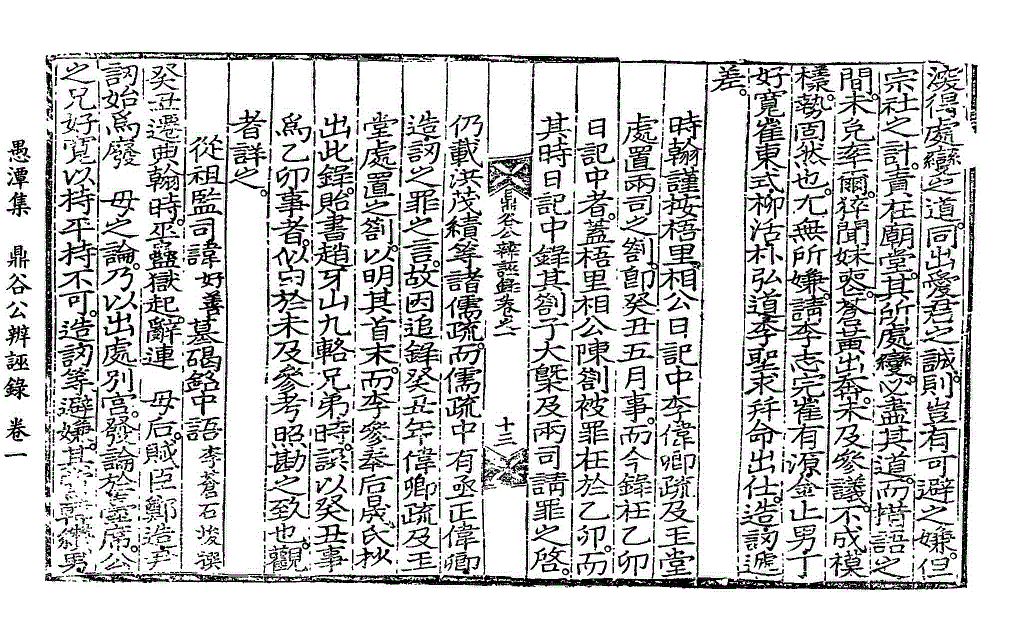 深得处变之道。同出爱君之诚。则岂有可避之嫌。但宗社之计。责在庙堂。其所处变。必尽其道。而措语之间。未免率尔。猝闻妹丧。苍黄出奔。未及参议。不成模样。势固然也。尤无所嫌。请李志完,崔有源,金止男,丁好宽,崔东式,柳活,朴弘道,李圣求并命出仕。造,讱递差。
深得处变之道。同出爱君之诚。则岂有可避之嫌。但宗社之计。责在庙堂。其所处变。必尽其道。而措语之间。未免率尔。猝闻妹丧。苍黄出奔。未及参议。不成模样。势固然也。尤无所嫌。请李志完,崔有源,金止男,丁好宽,崔东式,柳活,朴弘道,李圣求并命出仕。造,讱递差。时翰谨按梧里相公日记中李伟卿疏及玉堂处置两司之劄。即癸丑五月事。而今录在乙卯日记中者。盖梧里相公陈劄被罪在于乙卯。而其时日记中录其劄子大槩及两司请罪之启。仍载洪茂绩等诸儒疏。而儒疏中有亟正伟卿,造,讱之罪之言。故因追录癸丑年伟卿疏及玉堂处置之劄。以明其首末。而李参奉后晟氏抄出此录。贻书赵牙山九辂兄弟时。误以癸丑事为乙卯事者。似由于未及参考照勘之致也。观者详之。
从祖监司讳(好善)墓碣铭中语(李苍石埈撰)
癸丑迁典翰时。巫蛊狱起。辞连 母后。贼臣郑造,尹讱始为废 母之论。乃以出处别宫。发论于台席。公之兄好宽以持平持不可。造,讱等避嫌。其党韩缵男,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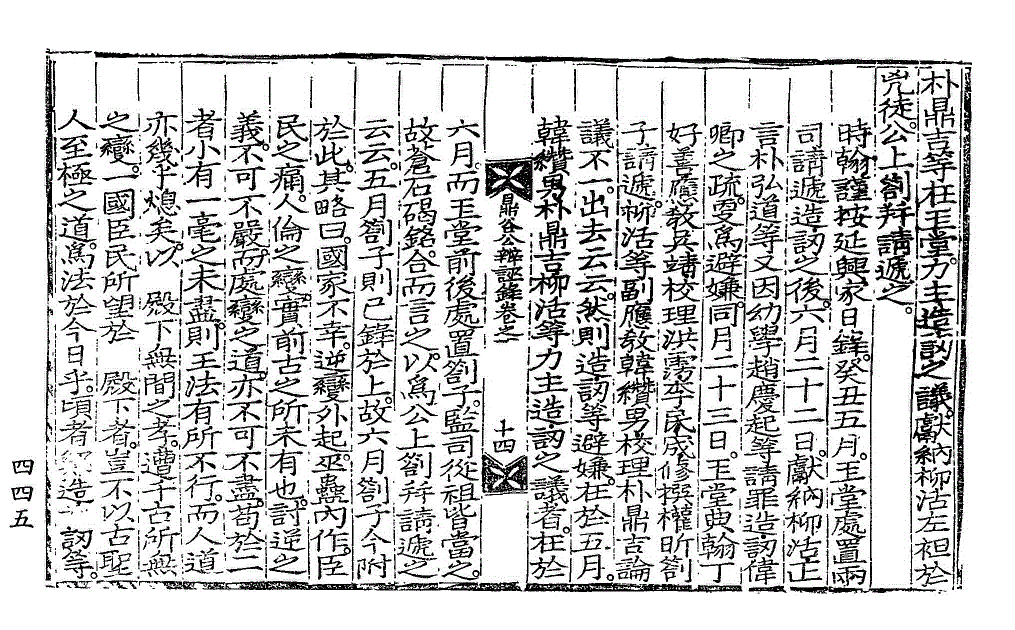 朴鼎吉等在玉堂。力主造,讱之议。献纳柳活左袒于凶徒。公上劄并请递之。
朴鼎吉等在玉堂。力主造,讱之议。献纳柳活左袒于凶徒。公上劄并请递之。时翰谨按延兴家日录。癸丑五月。玉堂处置两司请递造,讱之后。六月二十二日。献纳柳活,正言朴弘道等又因幼学赵庆起等请罪造,讱,伟卿之疏。更为避嫌。同月二十三日玉堂典翰丁好善,应教吴靖,校理洪霶,李民宬,修撰权昕劄子请递。柳活等副应教韩缵男,校理朴鼎吉论议不一。出去云云。然则造,讱等避嫌。在于五月。韩缵男,朴鼎吉,柳活等力主造,讱之议者。在于六月。而玉堂前后处置劄子。监司从祖皆当之。故苍石碣铭。合而言之。以为公上劄并请递之云云。五月劄子则已录于上。故六月劄子今附于此。其略曰。国家不幸。逆变外起。巫蛊内作。臣民之痛。人伦之变。实前古之所未有也。讨逆之义。不可不严。而处变之道。亦不可不尽。苟于二者小有一毫之未尽。则王法有所不行。而人道亦几乎熄矣。以 殿下无间之孝。遭千古所无之变。一国臣民所望于 殿下者。岂不以古圣人至极之道。为法于今日乎。顷者郑造,尹讱等。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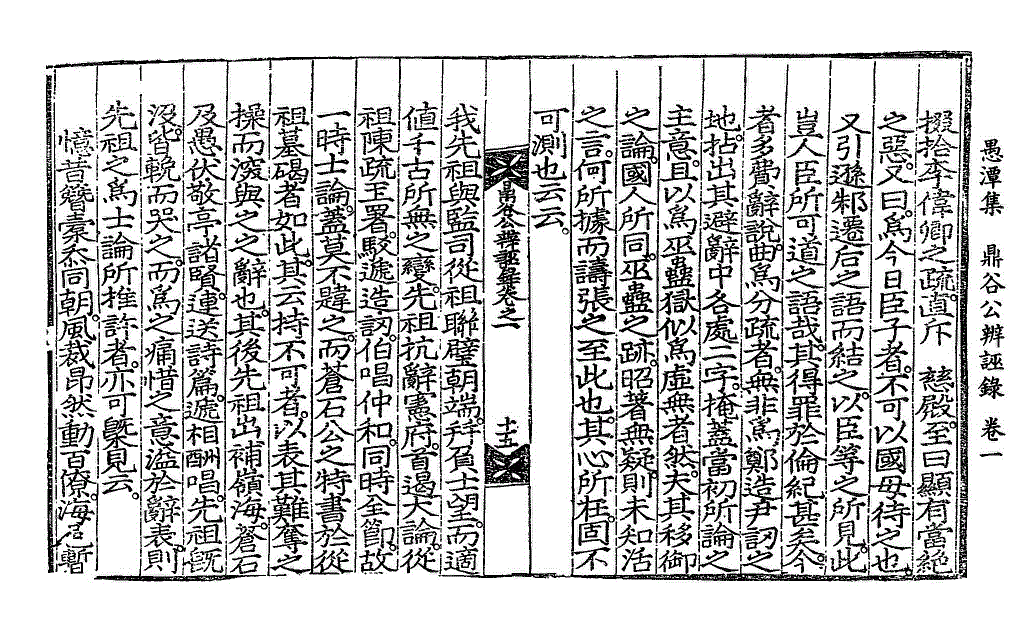 掇拾李伟卿之疏。直斥 慈殿。至曰显有当绝之恶。又曰。为今日臣子者。不可以国母待之也。又引逊邾迁后之语而结之。以臣等之所见。此岂人臣所可道之语哉。其得罪于伦纪甚矣。今者多费辞说。曲为分疏者。无非为郑造,尹讱之地。拈出其避辞中各处二字。掩盖当初所论之主意。且以为巫蛊狱似为虚无者然。夫其移御之论。国人所同。巫蛊之迹。昭著无疑。则未知活之言。何所据而诪张之至此也。其心所在。固不可测也云云。
掇拾李伟卿之疏。直斥 慈殿。至曰显有当绝之恶。又曰。为今日臣子者。不可以国母待之也。又引逊邾迁后之语而结之。以臣等之所见。此岂人臣所可道之语哉。其得罪于伦纪甚矣。今者多费辞说。曲为分疏者。无非为郑造,尹讱之地。拈出其避辞中各处二字。掩盖当初所论之主意。且以为巫蛊狱似为虚无者然。夫其移御之论。国人所同。巫蛊之迹。昭著无疑。则未知活之言。何所据而诪张之至此也。其心所在。固不可测也云云。我先祖与监司从祖联璧朝端。并负士望。而适值千古所无之变。先祖抗辞宪府。首遏大论。从祖陈疏玉署。驳递造,讱。伯唱仲和。同时全节。故一时士论。盖莫不韪之。而苍石公之特书于从祖墓碣者如此。其云持不可者。以表其难夺之操而深与之之辞也。其后先祖出补岭海。苍石及愚伏,敬亭诸贤。连送诗篇。递相酬唱。先祖既没。皆挽而哭之。而为之痛惜之意溢于辞表。则先祖之为士论所推许者。亦可槩见云。
忆昔簪橐忝同朝。风裁昂然动百僚。海邑暂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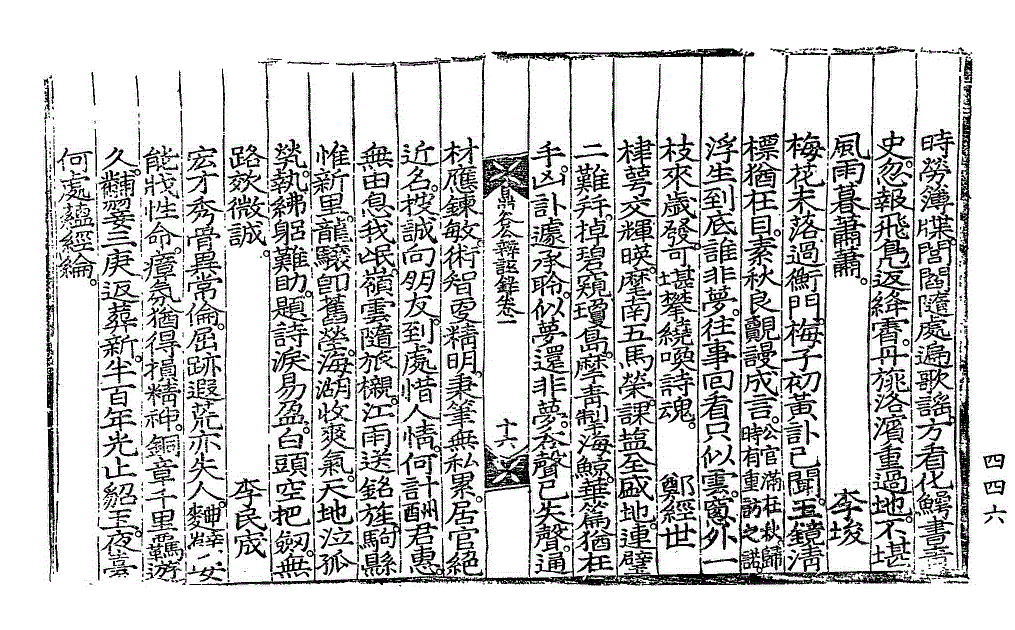 时劳簿牒。闾阎随处遍歌谣。方看化鳄书青史。忽报飞凫返绛霄。丹旐洛滨重过地。不堪风雨暮萧萧。(李埈)
时劳簿牒。闾阎随处遍歌谣。方看化鳄书青史。忽报飞凫返绛霄。丹旐洛滨重过地。不堪风雨暮萧萧。(李埈)梅花未落过衡门。梅子初黄讣已闻。玉镜清标犹在目。素秋良觌谩成言。(公官满在秋。归时有重访之诺。)浮生到底谁非梦。往事回看只似云。窗外一枝来岁发。可堪攀绕唤诗魂。(郑经世)
棣萼交辉映。麾南五马荣。课盐全盛地。连璧二难并。棹碧窥琼岛。摩青掣海鲸。华篇犹在手。凶讣遽承聆。似梦还非梦。吞声已失声。通材应鍊敏。术智更精明。秉笔无私累。居官绝近名。披诚向朋友。到处惜人情。何计酬君惠。无由息我氓。岭云随旅榇。江雨送铭旌。驹县惟新里。龙骧即旧茔。海湖收爽气。天地泣孤茕。执绋躬难助。题诗泪易盈。白头空把剑。无路效微诚。(李民宬)
宏才秀骨异常伦。屈迹遐荒亦失人。曲蘖安能戕性命。瘴氛犹得损精神。铜章千里羁游久。黼翣三庚返葬新。半百年光止貂玉。夜台何处蕴经纶。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7H 页
 诗礼家庭教泽隆。盈门鸑鷟桂成丛。两兄已去仙游继。三弟犹存世念空。衰病寡妻哀有尽。文明孝子庆无穷。同邻厚谊频书信。手迹那堪在箧中。(沈喜寿)
诗礼家庭教泽隆。盈门鸑鷟桂成丛。两兄已去仙游继。三弟犹存世念空。衰病寡妻哀有尽。文明孝子庆无穷。同邻厚谊频书信。手迹那堪在箧中。(沈喜寿)从祖进士讳好悌。公亦参馆儒李安真及权淰请斩造,讱,伟卿三贼之疏。我先祖昆李三人之于造,讱。其所痛斥而深嫉之者。若是其章章明著。而桐溪之疏。龙洲之文。乃反与造,讱混称。此所谓合水火冰炭于一器之中者也。是非之混淆。世或有之。而安有如是之讹舛也耶。
郑桐溪(蕴)甲寅疏
云云。顷者郑造,尹讱,丁好宽等。首发废妃杀弟之议。不议于同僚。不通于他司。不告于大臣。不询于诸宰。而窃发于完席之上。遽暴于避嫌之中。曾不若论一守令劾一庶官之为持难。此其心不难知矣。盖自近年以来。倖门一开。勋名太滥。贪功乐祸之徒。接迹而起。至以吾君之至亲。为自己富贵之饵。此如逐兽者挤人独走。冀得先杀之功。噫。为人臣子。是可忍耶云云。
时翰谨按当癸丑年间。永昌幽死。废论始发之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7L 页
 后。忠义之士忘身叫阍者。前后踵相接。如李安真,赵庆起,郑复亨,权淰,李命达,洪茂绩,郑泽雷,金孝诚诸人之疏不可殚记。而皆举伟卿,造,讱三贼为言。其后白沙,愚伏,苍石诸贤著述文字。及梧里李相,贰相姜公诸名家记录议论。如彼明白。而独桐溪一疏。乃为此无證之言。故论者以为桐溪之疏。各有所指。以废妃之论。罪造,讱。又以杀弟之议。归我先祖。有此混书云云。此虽似然。而知其事实者。犹可如是观之。不知事实者。有难分解看破。且出置之启。虽曰杀弟之权舆。而既已立异废论之后。则可见其本情。在君子论人之道。只谓之杀弟之议。尚云不可。何得与贼臣并驱于废妃杀弟之罪名也。试以桐溪疏及造,讱避辞参互考之。则造,讱避辞。为宗社之计。责在庙堂。臣等所论。罪合万殒。李志完立异之辞亦谓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云者。与桐溪疏所谓不告于大臣。不通于诸宰。窃发于完席之上。遽暴于避嫌之中者。正相符合。以此推之。桐溪之意。似以我先祖为同参于造,讱各处之避。故下语如此。而其后桐溪深自悔叹。至
后。忠义之士忘身叫阍者。前后踵相接。如李安真,赵庆起,郑复亨,权淰,李命达,洪茂绩,郑泽雷,金孝诚诸人之疏不可殚记。而皆举伟卿,造,讱三贼为言。其后白沙,愚伏,苍石诸贤著述文字。及梧里李相,贰相姜公诸名家记录议论。如彼明白。而独桐溪一疏。乃为此无證之言。故论者以为桐溪之疏。各有所指。以废妃之论。罪造,讱。又以杀弟之议。归我先祖。有此混书云云。此虽似然。而知其事实者。犹可如是观之。不知事实者。有难分解看破。且出置之启。虽曰杀弟之权舆。而既已立异废论之后。则可见其本情。在君子论人之道。只谓之杀弟之议。尚云不可。何得与贼臣并驱于废妃杀弟之罪名也。试以桐溪疏及造,讱避辞参互考之。则造,讱避辞。为宗社之计。责在庙堂。臣等所论。罪合万殒。李志完立异之辞亦谓宜与大臣百僚广议以处云者。与桐溪疏所谓不告于大臣。不通于诸宰。窃发于完席之上。遽暴于避嫌之中者。正相符合。以此推之。桐溪之意。似以我先祖为同参于造,讱各处之避。故下语如此。而其后桐溪深自悔叹。至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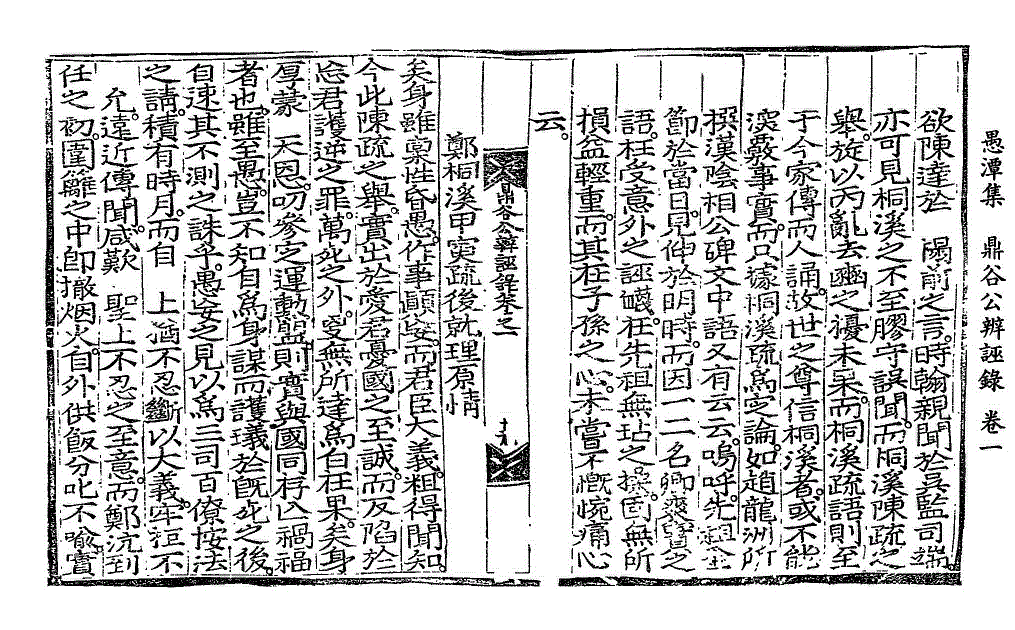 欲陈达于 榻前之言。时翰亲闻于吴监司端。亦可见桐溪之不至胶守误闻。而桐溪陈疏之举。旋以丙乱去豳之扰未果。而桐溪疏语则至于今家传而人诵。故世之尊信桐溪者。或不能深覈事实。而只据桐溪疏为定论。如赵龙洲所撰汉阴相公碑文中语又有云云。呜呼。先祖金节于当日。见伸于明时。而因一二名卿爽实之语。枉受意外之诬蔑。在先祖无玷之操。固无所损益轻重。而其在子孙之心。未尝不慨惋痛心云。
欲陈达于 榻前之言。时翰亲闻于吴监司端。亦可见桐溪之不至胶守误闻。而桐溪陈疏之举。旋以丙乱去豳之扰未果。而桐溪疏语则至于今家传而人诵。故世之尊信桐溪者。或不能深覈事实。而只据桐溪疏为定论。如赵龙洲所撰汉阴相公碑文中语又有云云。呜呼。先祖金节于当日。见伸于明时。而因一二名卿爽实之语。枉受意外之诬蔑。在先祖无玷之操。固无所损益轻重。而其在子孙之心。未尝不慨惋痛心云。郑桐溪甲寅疏后就理原情
矣身虽禀性昏愚。作事颠妄。而君臣大义。粗得闻知。今此陈疏之举。实出于爱君忧国之至诚。而反陷于忘君护逆之罪。万死之外。更无所达为白在果。矣身厚蒙 天恩。叨参定运勋盟。则实与国同存亡祸福者也。虽至愚。岂不知自为身谋而护㼁于既死之后。自速其不测之诛乎。愚妄之见以为三司百僚按法之请。积有时月。而自 上犹不忍断以大义。牢拒不 允。远近传闻。咸叹 圣上不忍之至意。而郑沆到任之初。围篱之中即撤烟火。自外供饭分叱不喻。实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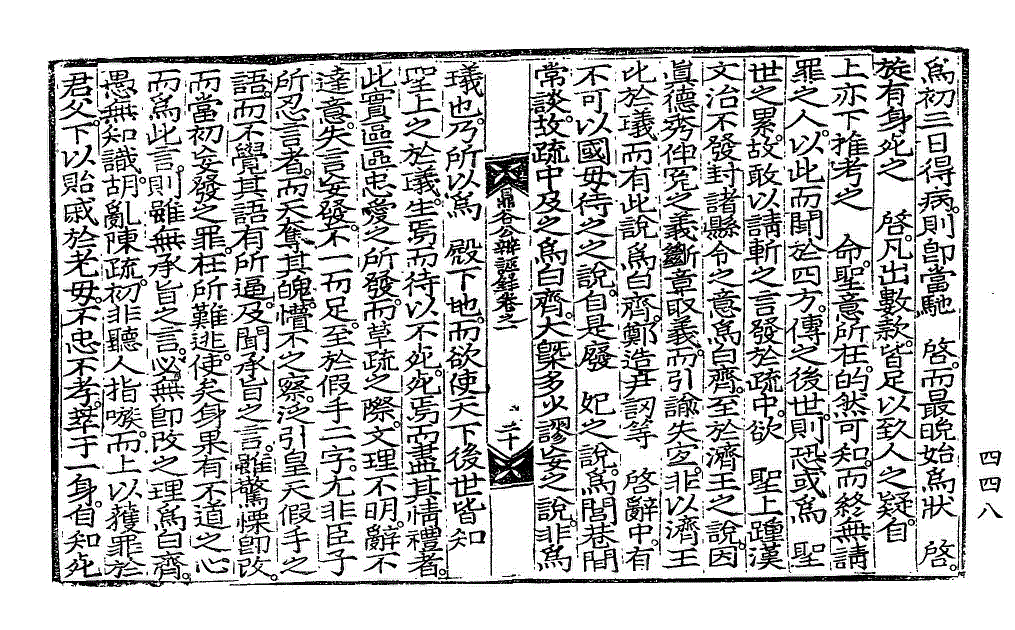 为初三日得病。则即当驰 启。而最晚始为状 启。旋有身死之 启。凡出数款。皆足以致人之疑。自 上亦下推考之 命。圣意所在。的然可知。而终无请罪之人。以此而闻于四方。传之后世。则恐或为 圣世之累。故敢以请斩之言发于疏中。欲 圣上踵汉文治不发封诸县令之意为白齐。至于济王之说。因真德秀伸冤之义断章取义。而引谕失宜。非以济王比于㼁而有此说为白齐。郑造,尹讱等 启辞中。有不可以国母待之之说。自是废 妃之说。为闾巷间常谈。故疏中及之为白齐。大槩多少谬妄之说。非为㼁也。乃所以为 殿下地。而欲使天下后世皆知 圣上之于㼁。生焉而待以不死。死焉而尽其情礼者。此实区区忠爱之所发。而草疏之际。文理不明。辞不达意。失言妄发。不一而足。至于假手二字。尤非臣子所忍言者。而天夺其魄。懵不之察。泛引皇天假手之语。而不觉其语有所逼。及闻承旨之言。虽惊慄即改。而当初妄发之罪。在所难逃。使矣身果有不道之心而为此言。则虽无承旨之言。必无即改之理为白齐。愚无知识。胡乱陈疏。初非听人指嗾。而上以获罪于君父。下以贻戚于老母。不忠不孝。萃于一身。自知死
为初三日得病。则即当驰 启。而最晚始为状 启。旋有身死之 启。凡出数款。皆足以致人之疑。自 上亦下推考之 命。圣意所在。的然可知。而终无请罪之人。以此而闻于四方。传之后世。则恐或为 圣世之累。故敢以请斩之言发于疏中。欲 圣上踵汉文治不发封诸县令之意为白齐。至于济王之说。因真德秀伸冤之义断章取义。而引谕失宜。非以济王比于㼁而有此说为白齐。郑造,尹讱等 启辞中。有不可以国母待之之说。自是废 妃之说。为闾巷间常谈。故疏中及之为白齐。大槩多少谬妄之说。非为㼁也。乃所以为 殿下地。而欲使天下后世皆知 圣上之于㼁。生焉而待以不死。死焉而尽其情礼者。此实区区忠爱之所发。而草疏之际。文理不明。辞不达意。失言妄发。不一而足。至于假手二字。尤非臣子所忍言者。而天夺其魄。懵不之察。泛引皇天假手之语。而不觉其语有所逼。及闻承旨之言。虽惊慄即改。而当初妄发之罪。在所难逃。使矣身果有不道之心而为此言。则虽无承旨之言。必无即改之理为白齐。愚无知识。胡乱陈疏。初非听人指嗾。而上以获罪于君父。下以贻戚于老母。不忠不孝。萃于一身。自知死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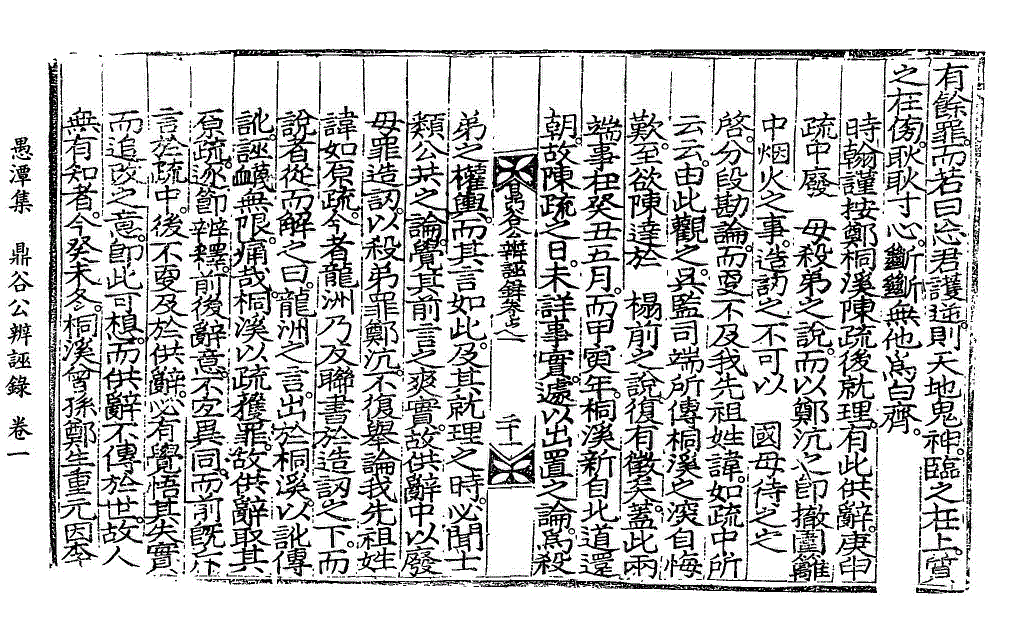 有馀罪。而若曰忘君护逆。则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耿耿寸心。断断无他为白齐。
有馀罪。而若曰忘君护逆。则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耿耿寸心。断断无他为白齐。时翰谨按郑桐溪陈疏后就理。有此供辞。庚申疏中废 母杀弟之说。而以郑沆之即撤围篱中烟火之事。造,讱之不可以 国母待之之 启。分段勘论。而更不及我先祖姓讳。如疏中所云云。由此观之。吴监司端所传桐溪之深自悔叹。至欲陈达于 榻前之说。复有徵矣。盖此两端事在癸丑五月。而甲寅年。桐溪新自北道还朝。故陈疏之日。未详事实。遽以出置之论。为杀弟之权舆。而其言如此。及其就理之时。必闻士类公共之论。觉其前言之爽实。故供辞中以废母罪造,讱。以杀弟罪郑沆。不复举论我先祖姓讳如原疏。今者龙洲乃反联书于造,讱之下。而说者从而解之曰。龙洲之言。出于桐溪。以讹传讹。诬蔑无限。痛哉。桐溪以疏获罪。故供辞取其原疏。逐节辨释。前后辞意。不宜异同。而前既斥言于疏中。后不更及于供辞。必有觉悟其失实而追改之意。即此可想。而供辞不传于世。故人无有知者。今癸未冬。桐溪曾孙郑生重元因李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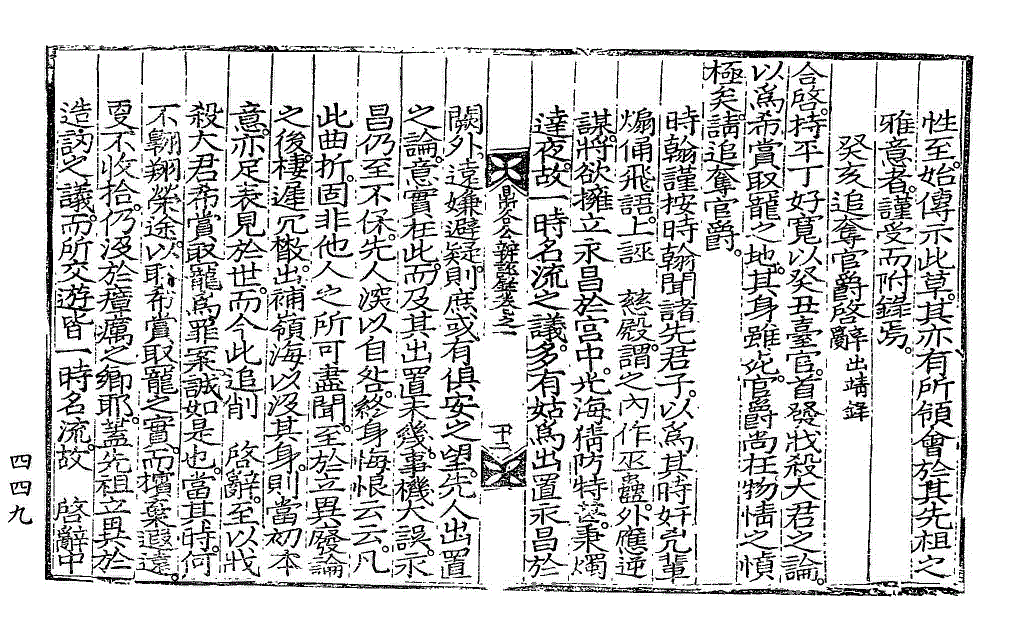 性至。始传示此草。其亦有所领会于其先祖之雅意者。谨受而附录焉。
性至。始传示此草。其亦有所领会于其先祖之雅意者。谨受而附录焉。癸亥追夺官爵启辞(出靖录)
合启。持平丁好宽以癸丑台官。首发戕杀大君之论。以为希赏取宠之地。其身虽死。官爵尚在。物情之愤极矣。请追夺官爵。
时翰谨按时翰闻诸先君子。以为其时奸凶辈煽俑飞语。上诬 慈殿。谓之内作巫蛊。外应逆谋。将欲拥立永昌于宫中。光海猜防特甚。秉烛达夜。故一时名流之议。多有姑为出置永昌于阙外。远嫌避疑。则庶或有俱安之望。先人出置之论。意实在此。而及其出置未几。事机大误。永昌仍至不保。先人深以自咎。终身悔恨云云。凡此曲折。固非他人之所可尽闻。至于立异废论之后。栖迟冗散。出补岭海以没其身。则当初本意。亦足表见于世。而今此追削 启辞。至以戕杀大君希赏取宠为罪案。诚如是也。当其时。何不翱翔荣途。以取希赏取宠之实。而摈弃遐远。更不收拾。仍没于瘴疠之乡耶。盖先祖立异于造,讱之议。而所交游皆一时名流。故 启辞中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0H 页
 亦不能驱之于奸党。而无他张皇胪列之罪过。其所勘成罪案之论。只如桐溪疏所谓为自己富贵之饵之言而已。后之人观此 启辞。参以先祖当时摈弃之事实。则其间情迹之大违于 启辞中语者。亦可以验之矣。
亦不能驱之于奸党。而无他张皇胪列之罪过。其所勘成罪案之论。只如桐溪疏所谓为自己富贵之饵之言而已。后之人观此 启辞。参以先祖当时摈弃之事实。则其间情迹之大违于 启辞中语者。亦可以验之矣。壬午先人除拜掌令时伸冤疏
伏以臣云云。伏念臣以先父臣好宽负罪明时。抱冤重泉。平生至痛。常煎迫于方寸间。欲一仰吁于 殿陛之下。而饮泣茹痛。悸惧而不敢陈者。于今二十年矣。至于今日。荣宠谬加。感激图报之外。宜不暇顾他。而只以臣父至冤不得少伸于泉壤。不肖如臣。何敢强颜于清班。微臣情势。实所惶蹙。宁不避万死之诛。一诉于天地父母之仁。伏乞 圣慈特垂矜察焉。臣窃伏念臣父之忝居侍从。实在 宣庙朝。递至癸丑年也。适拜持平。不幸遭千古所无之变。时故臣崔有源为大司宪。金止男为执义。逆臣造,讱遽发废置 母后之论。臣父与崔有源,金止男等联名避嫌。槩曰。慈殿岂人臣所可容议乎。宜参考古圣王处置之得宜者行之无愧于心。然后可免后世之讥议矣。凡人臣事君之道。纳吾君于无过之地。是第一义。何敢不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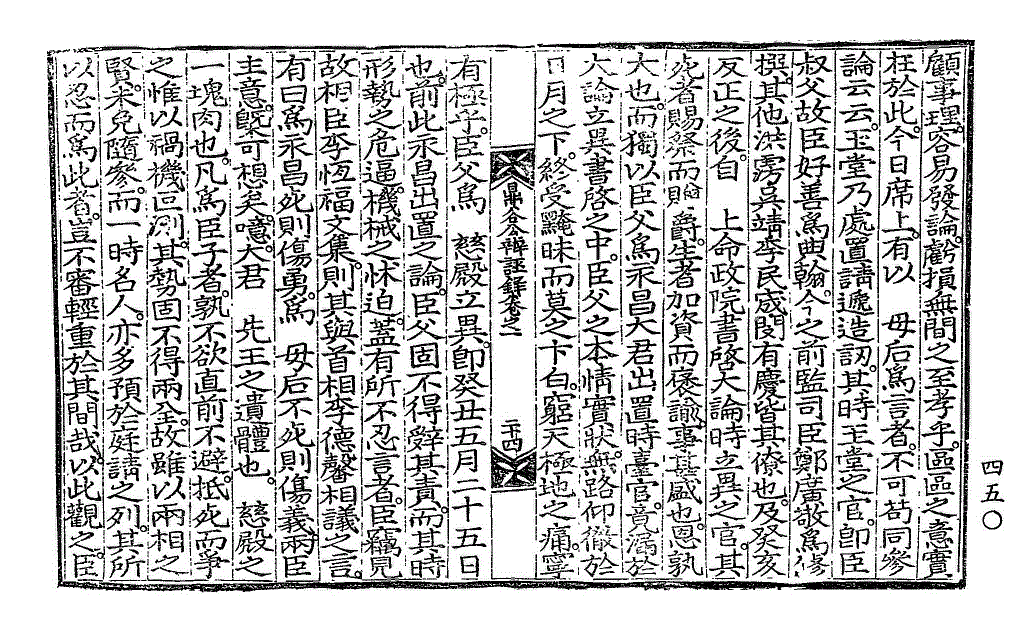 顾事理。容易发论。亏损无间之至孝乎。区区之意实在于此。今日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云云。玉堂乃处置请递造,讱。其时玉堂之官。即臣叔父故臣好善为典翰。今之前监司臣郑广敬为修撰。其他洪霶,吴靖,李民宬,闵有庆皆其僚也。及癸亥反正之后。自 上命政院书启大论时立异之官。其死者赐祭而赠爵。生者加资而褒谕。事甚盛也。恩孰大也。而独以臣父为永昌大君出置时台官。竟漏于大论立异书启之中。臣父之本情实状。无路仰彻于日月之下。终受黤昧而莫之卞白。穷天极地之痛。宁有极乎。臣父为 慈殿立异。即癸丑五月二十五日也。前此永昌出置之论。臣父固不得辞其责。而其时形势之危逼。机械之怵迫。盖有所不忍言者。臣窃见故相臣李恒福文集。则其与首相李德馨相议之言。有曰为永昌死则伤勇。为 母后不死则伤义。两臣主意。槩可想矣。噫。大君 先王之遗体也。 慈殿之一块肉也。凡为臣子者。孰不欲直前不避。抵死而争之惟以祸机叵测。其势固不得两全。故虽以两相之贤。未免随参。而 一时名人。亦多预于庭请之列。其所以忍而为此者。岂不审轻重于其间哉。以此观之。臣
顾事理。容易发论。亏损无间之至孝乎。区区之意实在于此。今日席上。有以 母后为言者。不可苟同参论云云。玉堂乃处置请递造,讱。其时玉堂之官。即臣叔父故臣好善为典翰。今之前监司臣郑广敬为修撰。其他洪霶,吴靖,李民宬,闵有庆皆其僚也。及癸亥反正之后。自 上命政院书启大论时立异之官。其死者赐祭而赠爵。生者加资而褒谕。事甚盛也。恩孰大也。而独以臣父为永昌大君出置时台官。竟漏于大论立异书启之中。臣父之本情实状。无路仰彻于日月之下。终受黤昧而莫之卞白。穷天极地之痛。宁有极乎。臣父为 慈殿立异。即癸丑五月二十五日也。前此永昌出置之论。臣父固不得辞其责。而其时形势之危逼。机械之怵迫。盖有所不忍言者。臣窃见故相臣李恒福文集。则其与首相李德馨相议之言。有曰为永昌死则伤勇。为 母后不死则伤义。两臣主意。槩可想矣。噫。大君 先王之遗体也。 慈殿之一块肉也。凡为臣子者。孰不欲直前不避。抵死而争之惟以祸机叵测。其势固不得两全。故虽以两相之贤。未免随参。而 一时名人。亦多预于庭请之列。其所以忍而为此者。岂不审轻重于其间哉。以此观之。臣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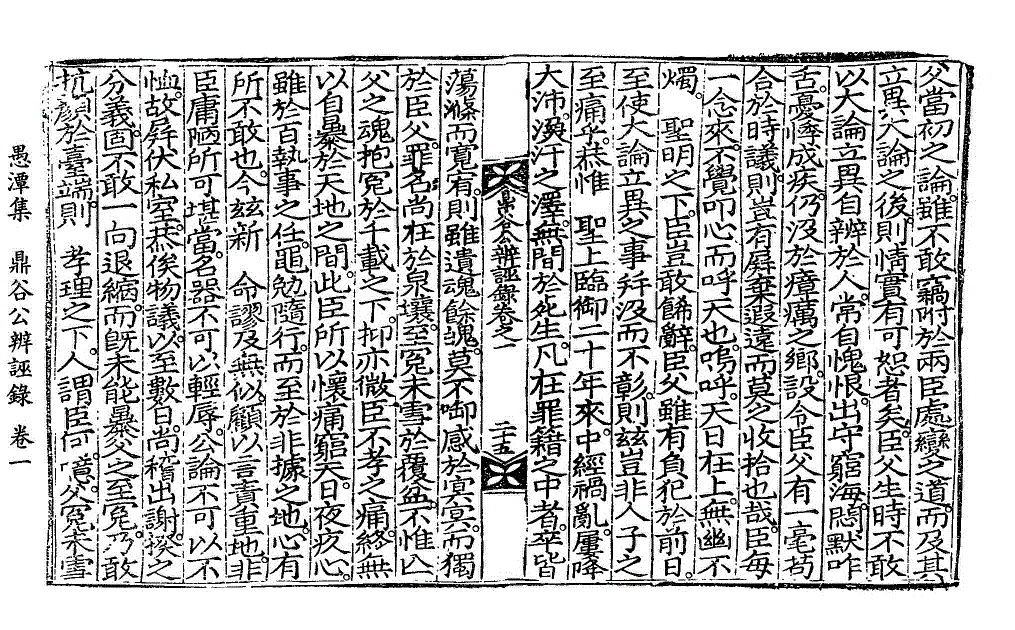 父当初之论。虽不敢窃附于两臣处变之道。而及其立异大论之后。则情实有可恕者矣。臣父生时不敢以大论立异自辨于人。常自愧恨。出守穷海。闷默咋舌。忧悸成疾。仍没于瘴疠之乡。设令臣父有一毫苟合于时议。则岂有屏弃遐远而莫之收拾也哉。臣每一念来。不觉叩心而呼天也。呜呼。天日在上。无幽不烛。 圣明之下。臣岂敢饰辞。臣父虽有负犯于前日。至使大论立异之事拜没而不彰。则玆岂非人子之至痛乎。恭惟 圣上临御二十年来。中经祸乱。屡降大沛。涣汗之泽。无间于死生。凡在罪籍之中者。卒皆荡涤而宽宥。则虽遗魂馀魄。莫不衔感于冥冥。而独于臣父。罪名尚在于泉壤。至冤未雪于覆盆。不惟亡父之魂抱冤于千载之下。抑亦微臣不孝之痛。终无以自暴于天地之间。此臣所以怀痛穷天。日夜疚心。虽于百执事之任。黾勉随行。而至于非据之地。心有所不敢也。今玆新 命谬及无似。顾以言责重地。非臣庸陋所可堪当。名器不可以轻辱。公论不可以不恤。故屏伏私室。恭俟物议。以至数日。尚稽出谢。揆之分义。固不敢一向退缩。而既未能暴父之至冤。乃敢抗颜于台端。则 孝理之下。人谓臣何。噫。父冤未雪
父当初之论。虽不敢窃附于两臣处变之道。而及其立异大论之后。则情实有可恕者矣。臣父生时不敢以大论立异自辨于人。常自愧恨。出守穷海。闷默咋舌。忧悸成疾。仍没于瘴疠之乡。设令臣父有一毫苟合于时议。则岂有屏弃遐远而莫之收拾也哉。臣每一念来。不觉叩心而呼天也。呜呼。天日在上。无幽不烛。 圣明之下。臣岂敢饰辞。臣父虽有负犯于前日。至使大论立异之事拜没而不彰。则玆岂非人子之至痛乎。恭惟 圣上临御二十年来。中经祸乱。屡降大沛。涣汗之泽。无间于死生。凡在罪籍之中者。卒皆荡涤而宽宥。则虽遗魂馀魄。莫不衔感于冥冥。而独于臣父。罪名尚在于泉壤。至冤未雪于覆盆。不惟亡父之魂抱冤于千载之下。抑亦微臣不孝之痛。终无以自暴于天地之间。此臣所以怀痛穷天。日夜疚心。虽于百执事之任。黾勉随行。而至于非据之地。心有所不敢也。今玆新 命谬及无似。顾以言责重地。非臣庸陋所可堪当。名器不可以轻辱。公论不可以不恤。故屏伏私室。恭俟物议。以至数日。尚稽出谢。揆之分义。固不敢一向退缩。而既未能暴父之至冤。乃敢抗颜于台端。则 孝理之下。人谓臣何。噫。父冤未雪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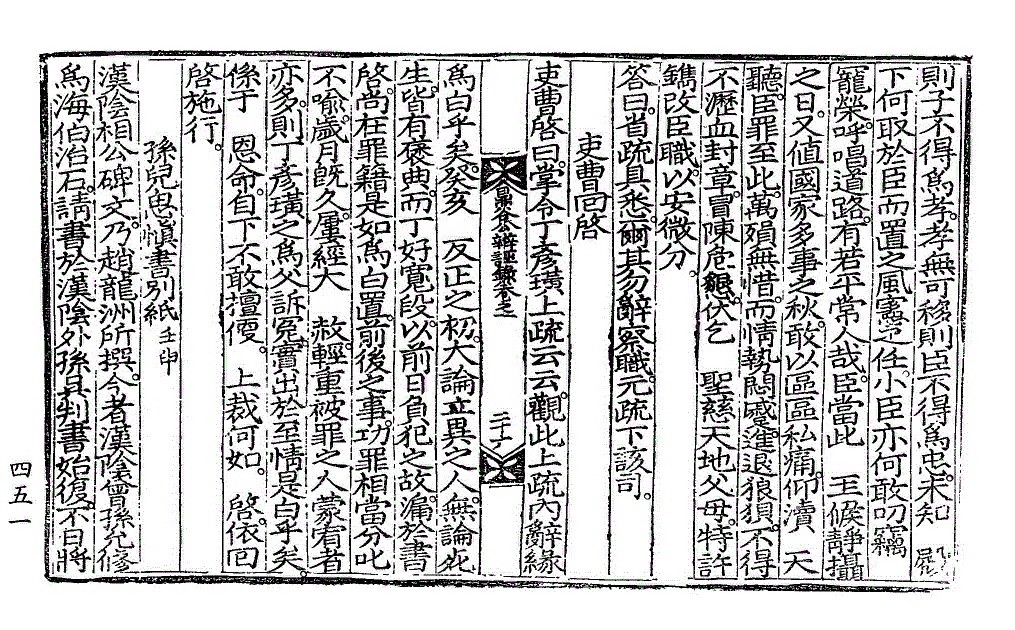 则子不得为孝。孝无可移则臣不得为忠。未知 殿下何取于臣而置之风宪之任。小臣亦何敢叨窃 宠荣。呼唱道路。有若平常人哉。臣当此 玉候静摄之日。又值国家多事之秋。敢以区区私痛。仰渎 天听。臣罪至此。万殒无惜。而情势闷蹙。进退狼狈。不得不沥血封章。冒陈危恳。伏乞 圣慈天地父母。特许镌改臣职。以安微分。
则子不得为孝。孝无可移则臣不得为忠。未知 殿下何取于臣而置之风宪之任。小臣亦何敢叨窃 宠荣。呼唱道路。有若平常人哉。臣当此 玉候静摄之日。又值国家多事之秋。敢以区区私痛。仰渎 天听。臣罪至此。万殒无惜。而情势闷蹙。进退狼狈。不得不沥血封章。冒陈危恳。伏乞 圣慈天地父母。特许镌改臣职。以安微分。答曰。省疏具悉。尔其勿辞察职。元疏下该司。
吏曹回启
吏曹启曰。掌令丁彦璜上疏云云。观此上疏内辞缘为白乎矣。癸亥 反正之初。大论立异之人。无论死生。皆有褒典。而丁好宽段。以前日负犯之故。漏于书启。尚在罪籍是如为白置。前后之事。功罪相当分叱不喻。岁月既久。屡经大 赦。轻重被罪之人蒙宥者亦多。则丁彦璜之为父诉冤。实出于至情是白乎矣。系于 恩命。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启。依回启施行。
孙儿思慎书别纸(壬申)
汉阴相公碑文。乃赵龙洲所撰。今者汉阴曾孙允修为海伯治石。请书于汉阴外孙吴判书始复。不日将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2H 页
 为竖立。宗孙李正字寿仁来言其间文字。有害于君家。考其事实。亦涉可疑。而今难变通云云。取见其文。则至癸丑事。乃书高祖父主名字。至谓郑造,尹讱,丁某等共发废母之论。看来极可痛骇。盖龙洲一生偏信桐溪。故因桐溪之误闻。又为祖述而言之。桐溪一疏。已矣难追。而既已据实伸白。举世皆知之。后又复转相袭谬。刻诸金石。非但为子孙之至痛。事之无据。莫此为甚。故与汉阴子孙相议。则李正字以为汉阴一生知己是白沙。知其时实状。亦莫如白沙。而白沙之撰志。元不举论。愚伏所制行状亦无之。而此独并举。可知其只信桐溪之说。删去无妨。而一家诸议不一云云。就见诸子孙。详言其前后事实。则亦似为然。而终以为龙洲生时。李平昌象鼎氏累质而不见听。及今龙洲汲后追改。有所未安。且此处子孙虽删去。而龙洲文集若仍存刊出。则必有他人情外之谤。彼此俱不好。当博询广议而处之云云。而今人偏信龙洲而未谙故事。有难容易解惑。当此之机。必须极力辨破。可免后世之诬蔑。故欲将家乘之可据者及诸人文字。以为辨破之地。而洪判书制曾祖父主行状中。亦载伸雪之疏。故欲持来为證。行状及杂录册伸
为竖立。宗孙李正字寿仁来言其间文字。有害于君家。考其事实。亦涉可疑。而今难变通云云。取见其文。则至癸丑事。乃书高祖父主名字。至谓郑造,尹讱,丁某等共发废母之论。看来极可痛骇。盖龙洲一生偏信桐溪。故因桐溪之误闻。又为祖述而言之。桐溪一疏。已矣难追。而既已据实伸白。举世皆知之。后又复转相袭谬。刻诸金石。非但为子孙之至痛。事之无据。莫此为甚。故与汉阴子孙相议。则李正字以为汉阴一生知己是白沙。知其时实状。亦莫如白沙。而白沙之撰志。元不举论。愚伏所制行状亦无之。而此独并举。可知其只信桐溪之说。删去无妨。而一家诸议不一云云。就见诸子孙。详言其前后事实。则亦似为然。而终以为龙洲生时。李平昌象鼎氏累质而不见听。及今龙洲汲后追改。有所未安。且此处子孙虽删去。而龙洲文集若仍存刊出。则必有他人情外之谤。彼此俱不好。当博询广议而处之云云。而今人偏信龙洲而未谙故事。有难容易解惑。当此之机。必须极力辨破。可免后世之诬蔑。故欲将家乘之可据者及诸人文字。以为辨破之地。而洪判书制曾祖父主行状中。亦载伸雪之疏。故欲持来为證。行状及杂录册伸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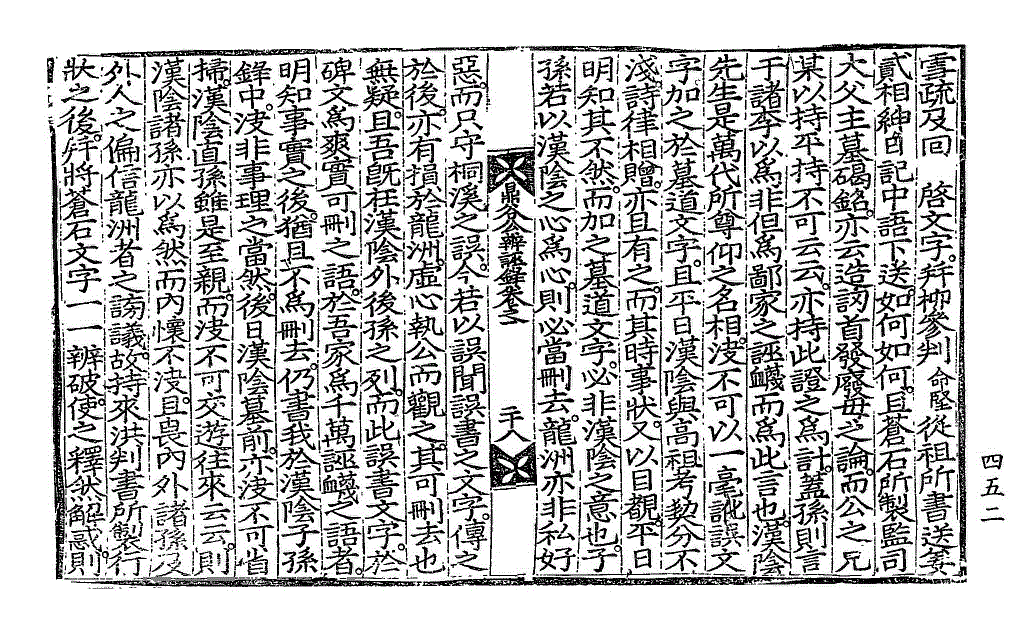 雪疏及回 启文字。并柳参判(命坚)从祖所书送姜贰相绅日记中语下送。如何如何。且苍石所制监司大父主墓碣铭。亦云造,讱首发废母之论。而公之兄某以持平持不可云云。亦持此證之为计。盖孙则言于诸李以为非但为鄙家之诬蔑而为此言也。汉阴先生是万代所尊仰之名相。决不可以一毫讹误文字。加之于墓道文字。且平日汉阴与高祖考契分不浅。诗律相赠。亦且有之。而其时事状。又以目睹。平日明知其不然。而加之墓道文字。必非汉阴之意也。子孙若以汉阴之心为心。则必当删去。龙洲亦非私好恶。而只守桐溪之误。今若以误闻误书之文字。传之于后。亦有损于龙洲。虚心执公而观之。其可删去也无疑。且吾既在汉阴外后孙之列。而此误书文字。于碑文为爽实可删之语。于吾家为千万诬蔑之语者。明知事实之后。犹且不为删去。仍书我于汉阴子孙录中。决非事理之当然。后日汉阴墓前。亦决不可省扫。汉阴直孙虽是至亲。而决不可交游往来云云。则汉阴诸孙亦以为然而内怀不决。且畏内外诸孙及外人之偏信龙洲者之谤议。故持来洪判书所制行状之后。并将苍石文字一一辨破。使之释然解惑。则
雪疏及回 启文字。并柳参判(命坚)从祖所书送姜贰相绅日记中语下送。如何如何。且苍石所制监司大父主墓碣铭。亦云造,讱首发废母之论。而公之兄某以持平持不可云云。亦持此證之为计。盖孙则言于诸李以为非但为鄙家之诬蔑而为此言也。汉阴先生是万代所尊仰之名相。决不可以一毫讹误文字。加之于墓道文字。且平日汉阴与高祖考契分不浅。诗律相赠。亦且有之。而其时事状。又以目睹。平日明知其不然。而加之墓道文字。必非汉阴之意也。子孙若以汉阴之心为心。则必当删去。龙洲亦非私好恶。而只守桐溪之误。今若以误闻误书之文字。传之于后。亦有损于龙洲。虚心执公而观之。其可删去也无疑。且吾既在汉阴外后孙之列。而此误书文字。于碑文为爽实可删之语。于吾家为千万诬蔑之语者。明知事实之后。犹且不为删去。仍书我于汉阴子孙录中。决非事理之当然。后日汉阴墓前。亦决不可省扫。汉阴直孙虽是至亲。而决不可交游往来云云。则汉阴诸孙亦以为然而内怀不决。且畏内外诸孙及外人之偏信龙洲者之谤议。故持来洪判书所制行状之后。并将苍石文字一一辨破。使之释然解惑。则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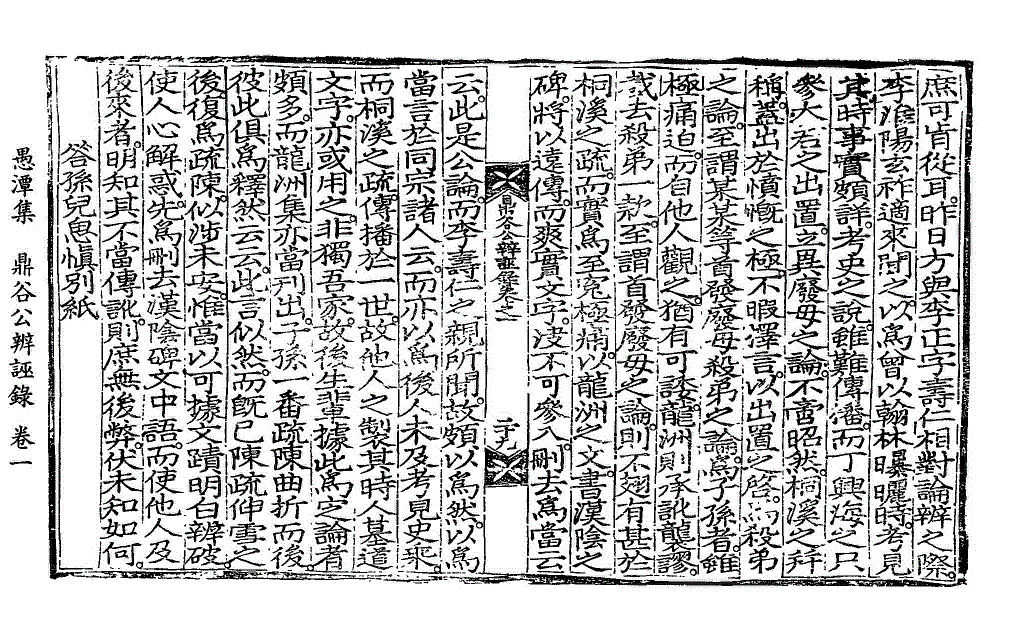 庶可肯从耳。昨日方与李正字寿仁相对论辨之际。李淮阳玄祚适来闻之。以为曾以翰林曝晒时。考见其时事实颇详。考史之说。虽难传播。而丁兴海之只参大君之出置。立异废母之论。不啻昭然。桐溪之并称。盖出于愤慨之极。不暇择言。以出置之启。为杀弟之论。至谓某某等首发废母杀弟之论。为子孙者。虽极痛迫。而自他人观之。犹有可诿。龙洲则承讹袭谬。截去杀弟一款。至谓首发废母之论。则不翅有甚于桐溪之疏。而实为至冤极痛。以龙洲之文。书汉阴之碑。将以远传。而爽实文字。决不可参入。删去为当云云。此是公论。而李寿仁之亲所闻。故颇以为然。以为当言于同宗诸人云。而亦以为后人未及考见史乘。而桐溪之疏。传播于一世。故他人之制其时人墓道文字。亦或用之。非独吾家。故后生辈据此为定论者颇多。而龙洲集亦当刊出。子孙一番疏陈曲折而后。彼此俱为释然云云。此言似然。而既已陈疏伸雪之后。复为疏陈。似涉未安。惟当以可据文迹明白辨破。使人心解惑。先为删去汉阴碑文中语。而使他人及后来者。明知其不当传讹。则庶无后弊。伏未知如何。
庶可肯从耳。昨日方与李正字寿仁相对论辨之际。李淮阳玄祚适来闻之。以为曾以翰林曝晒时。考见其时事实颇详。考史之说。虽难传播。而丁兴海之只参大君之出置。立异废母之论。不啻昭然。桐溪之并称。盖出于愤慨之极。不暇择言。以出置之启。为杀弟之论。至谓某某等首发废母杀弟之论。为子孙者。虽极痛迫。而自他人观之。犹有可诿。龙洲则承讹袭谬。截去杀弟一款。至谓首发废母之论。则不翅有甚于桐溪之疏。而实为至冤极痛。以龙洲之文。书汉阴之碑。将以远传。而爽实文字。决不可参入。删去为当云云。此是公论。而李寿仁之亲所闻。故颇以为然。以为当言于同宗诸人云。而亦以为后人未及考见史乘。而桐溪之疏。传播于一世。故他人之制其时人墓道文字。亦或用之。非独吾家。故后生辈据此为定论者颇多。而龙洲集亦当刊出。子孙一番疏陈曲折而后。彼此俱为释然云云。此言似然。而既已陈疏伸雪之后。复为疏陈。似涉未安。惟当以可据文迹明白辨破。使人心解惑。先为删去汉阴碑文中语。而使他人及后来者。明知其不当传讹。则庶无后弊。伏未知如何。答孙儿思慎别纸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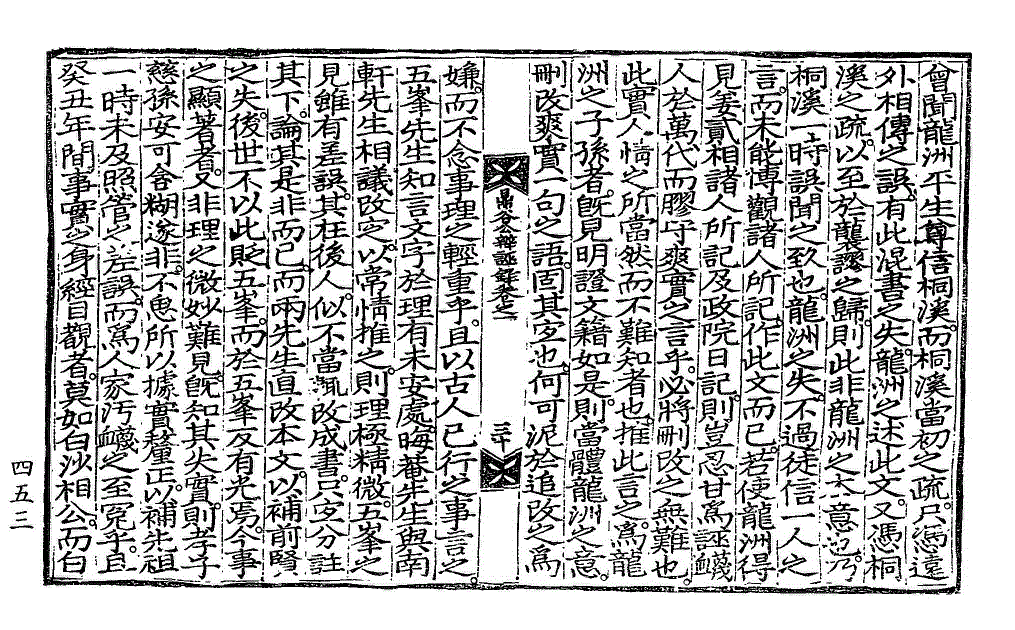 曾闻龙洲平生尊信桐溪。而桐溪当初之疏。只凭远外相传之误。有此混书之失。龙洲之述此文。又凭桐溪之疏。以至于袭谬之归。则此非龙洲之本意也。乃桐溪一时误闻之致也。龙洲之失。不过徒信一人之言。而未能博观诸人所记。作此文而已。若使龙洲得见姜贰相诸人所记及政院日记。则岂忍甘为诬蔑人于万代而胶守爽实之言乎。必将删改之无难也。此实人情之所当然而不难知者也。推此言之。为龙洲之子孙者。既见明證文籍如是。则当体龙洲之意。删改爽实一句之语。固其宜也。何可泥于追改之为嫌。而不念事理之轻重乎。且以古人已行之事言之。五峰先生知言文字于理有未安处。晦庵先生与南轩先生相议改定。以常情推之。则理极精微。五峰之见虽有差误。其在后人。似不当辄改成书。只宜分注其下。论其是非而已。而两先生直改本文。以补前贤之失。后世不以此贬五峰。而于五峰反有光焉。今事之显著者。又非理之微妙难见。既知其失实。则孝子慈孙安可含糊遂非。不思所以据实釐正。以补先祖一时未及照管之差误。而为人家污蔑之至冤乎。且癸丑年间事实之身经目睹者。莫如白沙相公。而白
曾闻龙洲平生尊信桐溪。而桐溪当初之疏。只凭远外相传之误。有此混书之失。龙洲之述此文。又凭桐溪之疏。以至于袭谬之归。则此非龙洲之本意也。乃桐溪一时误闻之致也。龙洲之失。不过徒信一人之言。而未能博观诸人所记。作此文而已。若使龙洲得见姜贰相诸人所记及政院日记。则岂忍甘为诬蔑人于万代而胶守爽实之言乎。必将删改之无难也。此实人情之所当然而不难知者也。推此言之。为龙洲之子孙者。既见明證文籍如是。则当体龙洲之意。删改爽实一句之语。固其宜也。何可泥于追改之为嫌。而不念事理之轻重乎。且以古人已行之事言之。五峰先生知言文字于理有未安处。晦庵先生与南轩先生相议改定。以常情推之。则理极精微。五峰之见虽有差误。其在后人。似不当辄改成书。只宜分注其下。论其是非而已。而两先生直改本文。以补前贤之失。后世不以此贬五峰。而于五峰反有光焉。今事之显著者。又非理之微妙难见。既知其失实。则孝子慈孙安可含糊遂非。不思所以据实釐正。以补先祖一时未及照管之差误。而为人家污蔑之至冤乎。且癸丑年间事实之身经目睹者。莫如白沙相公。而白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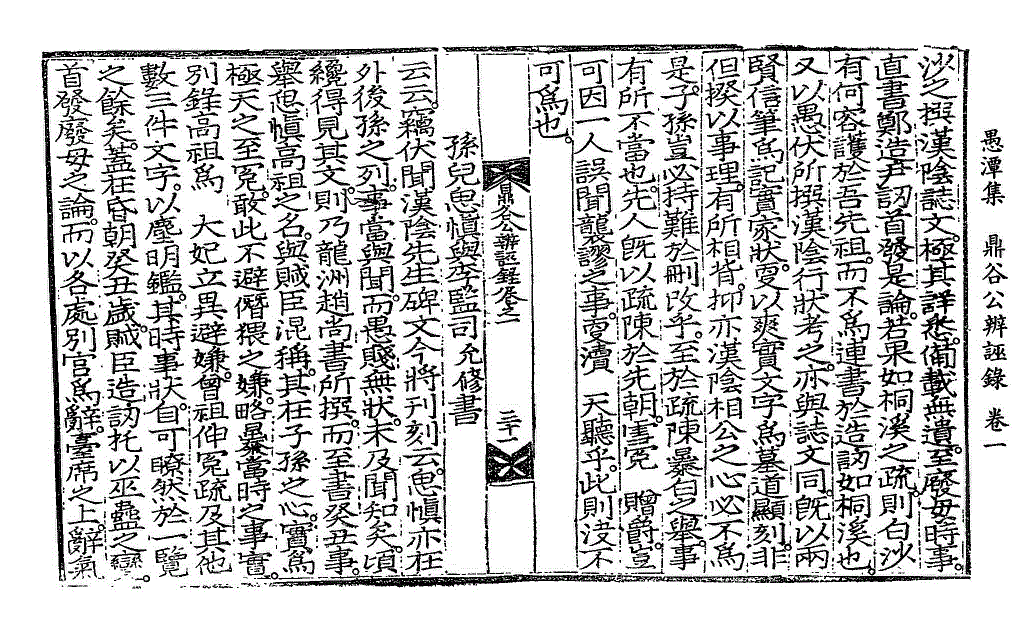 沙之撰汉阴志文。极其详悉。备载无遗。至废母时事。直书郑造,尹讱首发是论。若果如桐溪之疏。则白沙有何容护于吾先祖。而不为连书于造,讱如桐溪也。又以愚伏所撰汉阴行状考之。亦与志文同。既以两贤信笔为记实家状。更以爽实文字为墓道显刻。非但揆以事理。有所相背。抑亦汉阴相公之心必不为是。子孙岂必持难于删改乎。至于疏陈暴白之举。事有所不当也。先人既以疏陈于先朝。雪冤 赠爵。岂可因一人误闻袭谬之事。更渎 天听乎。此则决不可为也。
沙之撰汉阴志文。极其详悉。备载无遗。至废母时事。直书郑造,尹讱首发是论。若果如桐溪之疏。则白沙有何容护于吾先祖。而不为连书于造,讱如桐溪也。又以愚伏所撰汉阴行状考之。亦与志文同。既以两贤信笔为记实家状。更以爽实文字为墓道显刻。非但揆以事理。有所相背。抑亦汉阴相公之心必不为是。子孙岂必持难于删改乎。至于疏陈暴白之举。事有所不当也。先人既以疏陈于先朝。雪冤 赠爵。岂可因一人误闻袭谬之事。更渎 天听乎。此则决不可为也。孙儿思慎与李监司(允修)书
云云。窃伏闻汉阴先生碑文今将刊刻云。思慎亦在外后孙之列。事当与闻。而愚贱无状。未及闻知矣。顷才得见其文。则乃龙洲赵尚书所撰。而至书癸丑事。举思慎高祖之名。与贼臣混称。其在子孙之心。实为极天之至冤。敢此不避僭猥之嫌。略暴当时之事实。别录高祖为 大妃立异避嫌。曾祖伸冤疏及其他数三件文字。以尘明鉴。其时事状。自可瞭然于一览之馀矣。盖在昏朝癸丑岁。贼臣造,讱托以巫蛊之变。首发废母之论。而以各处别宫为辞。台席之上。辞气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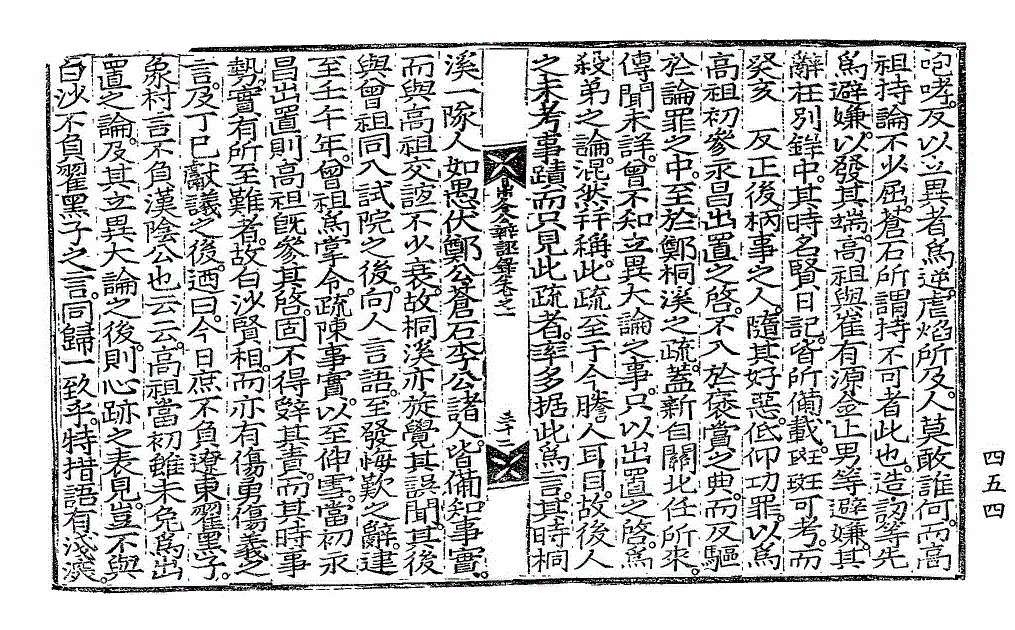 咆哮。反以立异者为逆。虐焰所及。人莫敢谁何。而高祖持论不少屈。苍石所谓持不可者此也。造,讱等先为避嫌。以发其端。高祖与崔有源,金止男等避嫌。其辞在别录中。其时名贤日记。皆所备载。斑斑可考。而癸亥 反正后柄事之人。随其好恶。低仰功罪。以为高祖初参永昌出置之启。不入于褒赏之典。而反驱于论罪之中。至于郑桐溪之疏。盖新自关北任所来。传闻未详。曾不知立异大论之事。只以出置之启。为杀弟之论。混然并称。此疏至于今誊人耳目。故后人之未考事迹而只见此疏者。率多据此为言。其时桐溪一队人如愚伏郑公,苍石李公诸人。皆备知事实。而与高祖交谊不少衰。故桐溪亦旋觉其误闻。其后与曾祖同入试院之后。向人言语。至发悔叹之辞。建至壬午年。曾祖为掌令。疏陈事实。以至伸雪。当初永昌出置则高祖既参其启。固不得辞其责。而其时事势。实有所至难者。故白沙贤相。而亦有伤勇伤义之言。及丁巳献议之后。乃曰。今日庶不负辽东翟黑子。象村言不负汉阴公也云云。高祖当初虽未免为出置之论。及其立异大论之后。则心迹之表见。岂不与白沙不负翟黑子之言。同归一致乎。特措语有浅深。
咆哮。反以立异者为逆。虐焰所及。人莫敢谁何。而高祖持论不少屈。苍石所谓持不可者此也。造,讱等先为避嫌。以发其端。高祖与崔有源,金止男等避嫌。其辞在别录中。其时名贤日记。皆所备载。斑斑可考。而癸亥 反正后柄事之人。随其好恶。低仰功罪。以为高祖初参永昌出置之启。不入于褒赏之典。而反驱于论罪之中。至于郑桐溪之疏。盖新自关北任所来。传闻未详。曾不知立异大论之事。只以出置之启。为杀弟之论。混然并称。此疏至于今誊人耳目。故后人之未考事迹而只见此疏者。率多据此为言。其时桐溪一队人如愚伏郑公,苍石李公诸人。皆备知事实。而与高祖交谊不少衰。故桐溪亦旋觉其误闻。其后与曾祖同入试院之后。向人言语。至发悔叹之辞。建至壬午年。曾祖为掌令。疏陈事实。以至伸雪。当初永昌出置则高祖既参其启。固不得辞其责。而其时事势。实有所至难者。故白沙贤相。而亦有伤勇伤义之言。及丁巳献议之后。乃曰。今日庶不负辽东翟黑子。象村言不负汉阴公也云云。高祖当初虽未免为出置之论。及其立异大论之后。则心迹之表见。岂不与白沙不负翟黑子之言。同归一致乎。特措语有浅深。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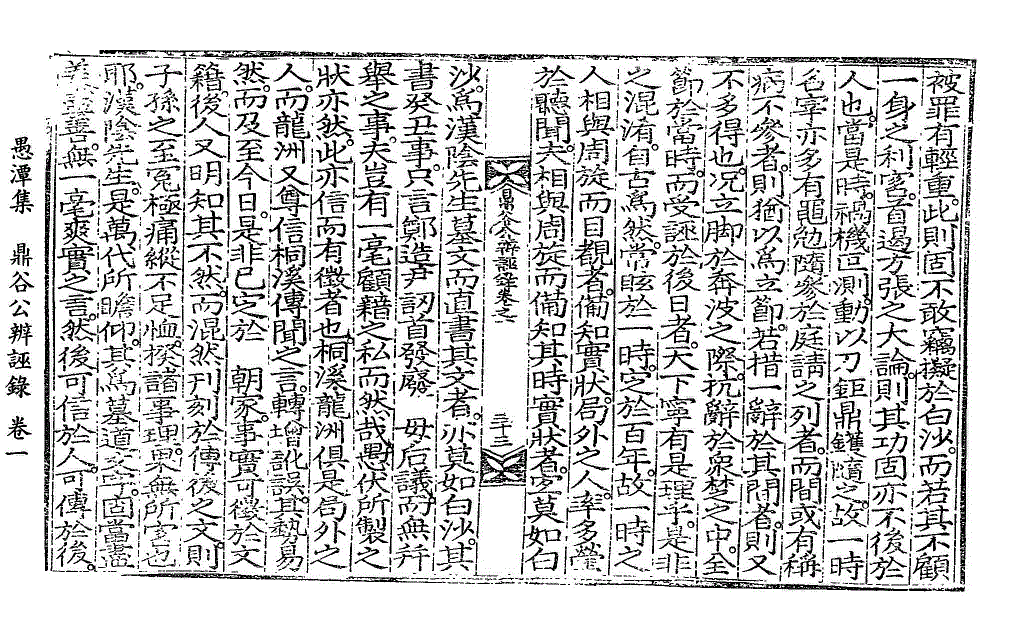 被罪有轻重。此则固不敢窃拟于白沙。而若其不顾一身之利害。首遏方张之大论。则其功固亦不后于人也。当是时。祸机叵测。动以刀钜鼎镬随之。故一时名宰亦多有黾勉随参于庭请之列者。而间或有称病不参者。则犹以为立节。若措一辞于其间者。则又不多得也。况立脚于奔波之际。抗辞于众楚之中。全节于当时。而受诬于后日者。天下宁有是理乎。是非之混淆。自古为然。常眩于一时。定于百年。故一时之人相与周旋而目睹者。备知实状。局外之人。率多莹于听闻。夫相与周旋而备知其时实状者。宜莫如白沙。为汉阴先生墓文而直书其文者。亦莫如白沙。其书癸丑事。只言郑造,尹讱首发废 母后议。而无并举之事。夫岂有一毫顾藉之私而然哉。愚伏所制之状亦然。此亦信而有徵者也。桐溪,龙洲俱是局外之人。而龙洲又尊信桐溪传闻之言。转增讹误。其势易然。而及至今日。是非已定于 朝家。事实可徵于文籍。后人又明知其不然。而混然刊刻于传后之文。则子孙之至冤极痛纵不足恤。揆诸事理。果无所害也耶。汉阴先生。是万代所瞻仰。其为墓道文字。固当尽美尽善。无一毫爽实之言。然后可信于人。可传于后。
被罪有轻重。此则固不敢窃拟于白沙。而若其不顾一身之利害。首遏方张之大论。则其功固亦不后于人也。当是时。祸机叵测。动以刀钜鼎镬随之。故一时名宰亦多有黾勉随参于庭请之列者。而间或有称病不参者。则犹以为立节。若措一辞于其间者。则又不多得也。况立脚于奔波之际。抗辞于众楚之中。全节于当时。而受诬于后日者。天下宁有是理乎。是非之混淆。自古为然。常眩于一时。定于百年。故一时之人相与周旋而目睹者。备知实状。局外之人。率多莹于听闻。夫相与周旋而备知其时实状者。宜莫如白沙。为汉阴先生墓文而直书其文者。亦莫如白沙。其书癸丑事。只言郑造,尹讱首发废 母后议。而无并举之事。夫岂有一毫顾藉之私而然哉。愚伏所制之状亦然。此亦信而有徵者也。桐溪,龙洲俱是局外之人。而龙洲又尊信桐溪传闻之言。转增讹误。其势易然。而及至今日。是非已定于 朝家。事实可徵于文籍。后人又明知其不然。而混然刊刻于传后之文。则子孙之至冤极痛纵不足恤。揆诸事理。果无所害也耶。汉阴先生。是万代所瞻仰。其为墓道文字。固当尽美尽善。无一毫爽实之言。然后可信于人。可传于后。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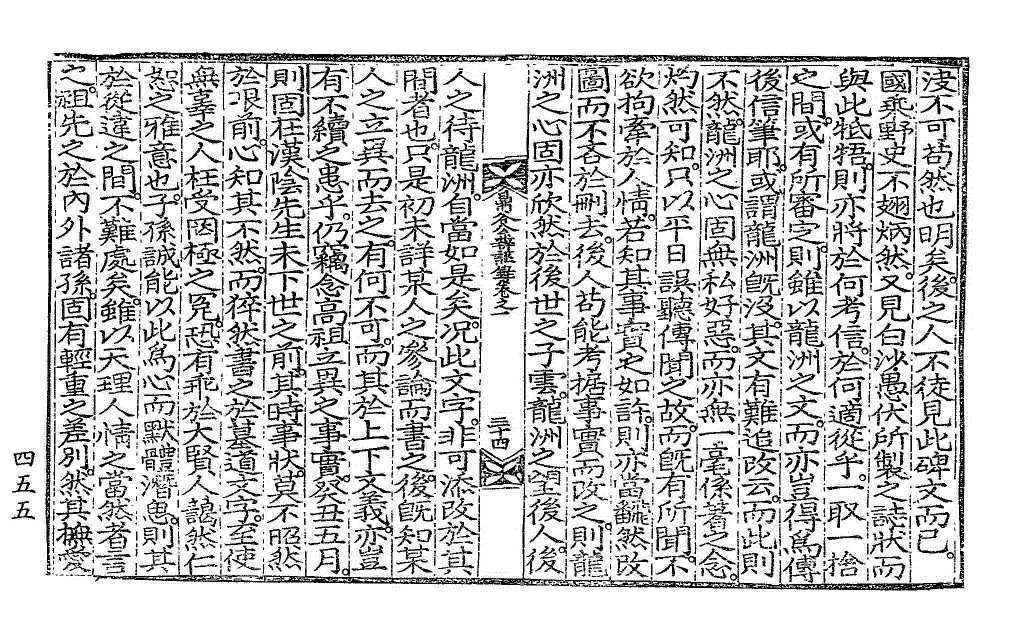 决不可苟然也明矣。后之人不徒见此碑文而已。 国乘野史不翅炳然。又见白沙,愚伏所制之志状而与此牴牾。则亦将于何考信。于何适从乎。一取一舍之间。或有所审定。则虽以龙洲之文。而亦岂得为传后信笔耶。或谓龙洲既没。其文有难追改云。而此则不然。龙洲之心固无私好恶。而亦无一毫系著之念。灼然可知。只以平日误听传闻之故。而既有所闻。不欲拘牵于人情。若知其事实之如许。则亦当翻然改图而不吝于删去。后人苟能考据事实而改之。则龙洲之心固亦欣然于后世之子云。龙洲之望后人。后人之待龙洲。自当如是矣。况此文字。非可添改于其间者也。只是初未详某人之参论而书之。后既知某人之立异而去之。有何不可。而其于上下文义。亦岂有不续之患乎。仍窃念高祖立异之事实。癸丑五月。则固在汉阴先生未下世之前。其时事状。莫不昭然于眼前。心知其不然。而猝然书之于墓道文字。至使无辜之人枉受罔极之冤。恐有乖于大贤人蔼然仁恕之雅意也。子孙诚能以此为心而默体潜思。则其于从违之间。不难处矣。虽以天理人情之当然者言之。祖先之于内外诸孙。固有轻重之差别。然其抚爱
决不可苟然也明矣。后之人不徒见此碑文而已。 国乘野史不翅炳然。又见白沙,愚伏所制之志状而与此牴牾。则亦将于何考信。于何适从乎。一取一舍之间。或有所审定。则虽以龙洲之文。而亦岂得为传后信笔耶。或谓龙洲既没。其文有难追改云。而此则不然。龙洲之心固无私好恶。而亦无一毫系著之念。灼然可知。只以平日误听传闻之故。而既有所闻。不欲拘牵于人情。若知其事实之如许。则亦当翻然改图而不吝于删去。后人苟能考据事实而改之。则龙洲之心固亦欣然于后世之子云。龙洲之望后人。后人之待龙洲。自当如是矣。况此文字。非可添改于其间者也。只是初未详某人之参论而书之。后既知某人之立异而去之。有何不可。而其于上下文义。亦岂有不续之患乎。仍窃念高祖立异之事实。癸丑五月。则固在汉阴先生未下世之前。其时事状。莫不昭然于眼前。心知其不然。而猝然书之于墓道文字。至使无辜之人枉受罔极之冤。恐有乖于大贤人蔼然仁恕之雅意也。子孙诚能以此为心而默体潜思。则其于从违之间。不难处矣。虽以天理人情之当然者言之。祖先之于内外诸孙。固有轻重之差别。然其抚爱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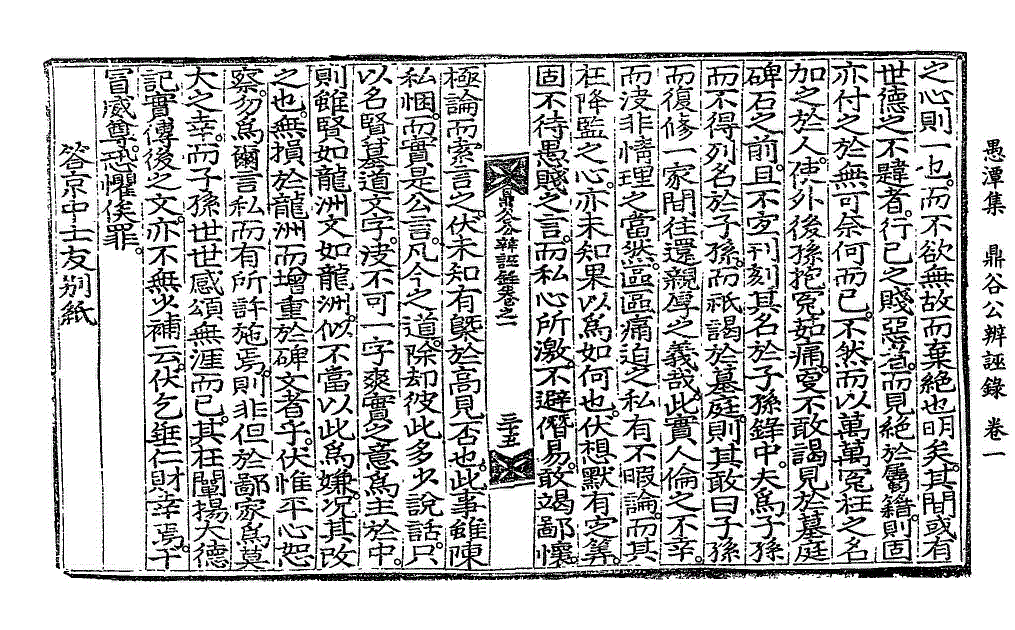 之心则一也。而不欲无故而弃绝也明矣。其间或有世德之不韪者。行己之贱恶者。而见绝于属籍。则固亦付之于无可奈何而已。不然而以万万冤枉之名加之于人。使外后孙抱冤茹痛。更不敢谒见于墓庭碑石之前。且不宜刊刻其名于子孙录中。夫为子孙而不得列名于子孙。而祇谒于墓庭。则其敢曰子孙而复修一家间往还亲厚之义哉。此实人伦之不幸。而决非情理之当然。区区痛迫之私有不暇论。而其在降监之心。亦未知果以为如何也。伏想默有定算。固不待愚贱之言。而私心所激不避僭易。敢竭鄙怀。极论而索言之。伏未知有槩于高见否也。此事虽陈私悃。而实是公言。凡今之道。除却彼此多少说话。只以名贤墓道文字。决不可一字爽实之意为主于中。则虽贤如龙洲文如龙洲。似不当以此为嫌。况其改之也。无损于龙洲而增重于碑文者乎。伏惟平心恕察。勿为尔言私而有所许施焉。则非但于鄙家为莫大之幸。而子孙世世感颂无涯而已。其在阐扬大德记实传后之文。亦不无少补云。伏乞垂仁财幸焉。干冒威尊。恐惧俟罪。
之心则一也。而不欲无故而弃绝也明矣。其间或有世德之不韪者。行己之贱恶者。而见绝于属籍。则固亦付之于无可奈何而已。不然而以万万冤枉之名加之于人。使外后孙抱冤茹痛。更不敢谒见于墓庭碑石之前。且不宜刊刻其名于子孙录中。夫为子孙而不得列名于子孙。而祇谒于墓庭。则其敢曰子孙而复修一家间往还亲厚之义哉。此实人伦之不幸。而决非情理之当然。区区痛迫之私有不暇论。而其在降监之心。亦未知果以为如何也。伏想默有定算。固不待愚贱之言。而私心所激不避僭易。敢竭鄙怀。极论而索言之。伏未知有槩于高见否也。此事虽陈私悃。而实是公言。凡今之道。除却彼此多少说话。只以名贤墓道文字。决不可一字爽实之意为主于中。则虽贤如龙洲文如龙洲。似不当以此为嫌。况其改之也。无损于龙洲而增重于碑文者乎。伏惟平心恕察。勿为尔言私而有所许施焉。则非但于鄙家为莫大之幸。而子孙世世感颂无涯而已。其在阐扬大德记实传后之文。亦不无少补云。伏乞垂仁财幸焉。干冒威尊。恐惧俟罪。答京中士友别纸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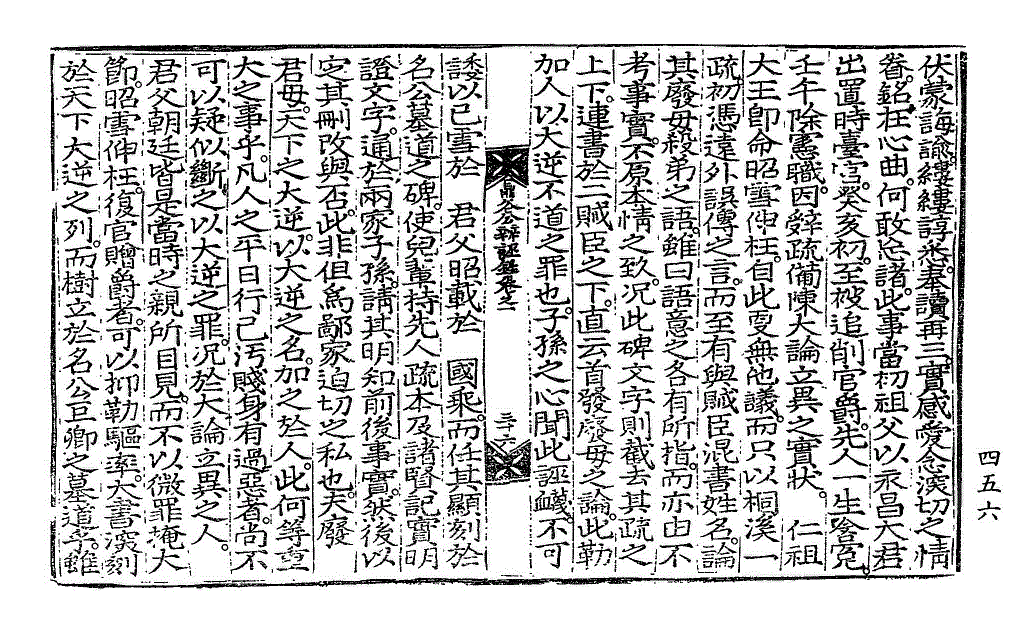 伏蒙诲谕。缕缕谆悉。奉读再三。实感爱念深切之情眷。铭在心曲。何敢忘诸。此事当初祖父以永昌大君出置时台官。癸亥初。至被追削官爵。先人一生含冤。壬午除宪职。因辞疏备陈大论立异之实状。 仁祖大王即命昭雪伸枉。自此更无他议。而只以桐溪一疏。初凭远外误传之言。而至有与贼臣混书姓名。论其废母杀弟之语。虽曰语意之各有所指。而亦由不考事实。不原本情之致。况此碑文字则截去其疏之上下。连书于二贼臣之下。直云首发废母之论。此勒加人以大逆不道之罪也。子孙之心闻此诬蔑。不可诿以已雪于 君父昭载于 国乘。而任其显刻于名公墓道之碑。使儿辈持先人疏本及诸贤记实明證文字。通于两家子孙。请其明知前后事实。然后以定其删改与否。此非但为鄙家迫切之私也。夫废 君母。天下之大逆。以大逆之名。加之于人。此何等重大之事乎。凡人之平日行己污贱身有过恶者。尚不可以疑似断之以大逆之罪。况于大论立异之人 君父朝廷皆是当时之亲所目见。而不以微罪掩大节。昭雪伸枉。复官赠爵者。可以抑勒驱率。大书深刻于天下大逆之列。而树立于名公巨卿之墓道乎。虽
伏蒙诲谕。缕缕谆悉。奉读再三。实感爱念深切之情眷。铭在心曲。何敢忘诸。此事当初祖父以永昌大君出置时台官。癸亥初。至被追削官爵。先人一生含冤。壬午除宪职。因辞疏备陈大论立异之实状。 仁祖大王即命昭雪伸枉。自此更无他议。而只以桐溪一疏。初凭远外误传之言。而至有与贼臣混书姓名。论其废母杀弟之语。虽曰语意之各有所指。而亦由不考事实。不原本情之致。况此碑文字则截去其疏之上下。连书于二贼臣之下。直云首发废母之论。此勒加人以大逆不道之罪也。子孙之心闻此诬蔑。不可诿以已雪于 君父昭载于 国乘。而任其显刻于名公墓道之碑。使儿辈持先人疏本及诸贤记实明證文字。通于两家子孙。请其明知前后事实。然后以定其删改与否。此非但为鄙家迫切之私也。夫废 君母。天下之大逆。以大逆之名。加之于人。此何等重大之事乎。凡人之平日行己污贱身有过恶者。尚不可以疑似断之以大逆之罪。况于大论立异之人 君父朝廷皆是当时之亲所目见。而不以微罪掩大节。昭雪伸枉。复官赠爵者。可以抑勒驱率。大书深刻于天下大逆之列。而树立于名公巨卿之墓道乎。虽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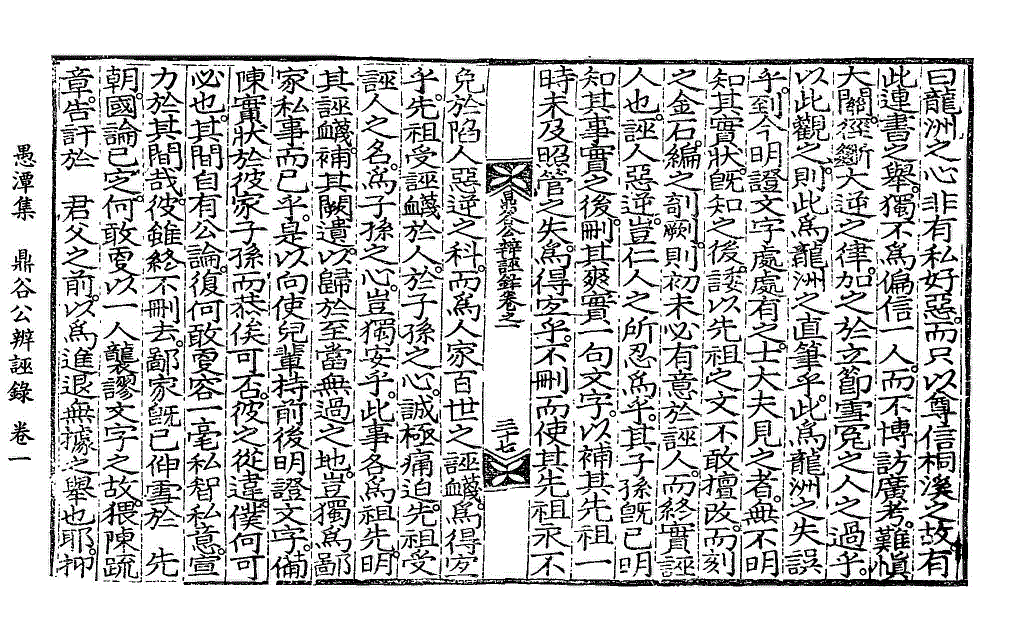 曰龙洲之心非有私好恶。而只以尊信桐溪之故。有此连书之举。独不为偏信一人。而不博访广考。难慎大关。径断大逆之律。加之于立节雪冤之人之过乎。以此观之。则此为龙洲之直笔乎。此为龙洲之失误乎。到今明證文字处处有之。士大夫见之者。无不明知其实状。既知之后。诿以先祖之文不敢擅改。而刻之金石。编之剞劂。则初未必有意于诬人。而终实诬人也。诬人恶逆。岂仁人之所忍为乎。其子孙既已明知其事实之后。删其爽实一句文字。以补其先祖一时未及照管之失。为得宜乎。不删而使其先祖永不免于陷人恶逆之科。而为人家百世之诬蔑。为得宜乎。先祖受诬蔑于人。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此事各为祖先。明其诬蔑。补其阙遗。以归于至当无过之地。岂独为鄙家私事而已乎。是以向使儿辈持前后明證文字。备陈实状于彼家子孙而恭俟可否。彼之从违。仆何可必也。其间自有公论。复何敢更容一毫私智私意。宣力于其间哉。彼虽终不删去。鄙家既已伸雪于 先朝。国论已定。何敢更以一人袭谬文字之故。猥陈疏章。告讦于 君父之前。以为进退无据之举也耶。抑
曰龙洲之心非有私好恶。而只以尊信桐溪之故。有此连书之举。独不为偏信一人。而不博访广考。难慎大关。径断大逆之律。加之于立节雪冤之人之过乎。以此观之。则此为龙洲之直笔乎。此为龙洲之失误乎。到今明證文字处处有之。士大夫见之者。无不明知其实状。既知之后。诿以先祖之文不敢擅改。而刻之金石。编之剞劂。则初未必有意于诬人。而终实诬人也。诬人恶逆。岂仁人之所忍为乎。其子孙既已明知其事实之后。删其爽实一句文字。以补其先祖一时未及照管之失。为得宜乎。不删而使其先祖永不免于陷人恶逆之科。而为人家百世之诬蔑。为得宜乎。先祖受诬蔑于人。于子孙之心。诚极痛迫。先祖受诬人之名。为子孙之心。岂独安乎。此事各为祖先。明其诬蔑。补其阙遗。以归于至当无过之地。岂独为鄙家私事而已乎。是以向使儿辈持前后明證文字。备陈实状于彼家子孙而恭俟可否。彼之从违。仆何可必也。其间自有公论。复何敢更容一毫私智私意。宣力于其间哉。彼虽终不删去。鄙家既已伸雪于 先朝。国论已定。何敢更以一人袭谬文字之故。猥陈疏章。告讦于 君父之前。以为进退无据之举也耶。抑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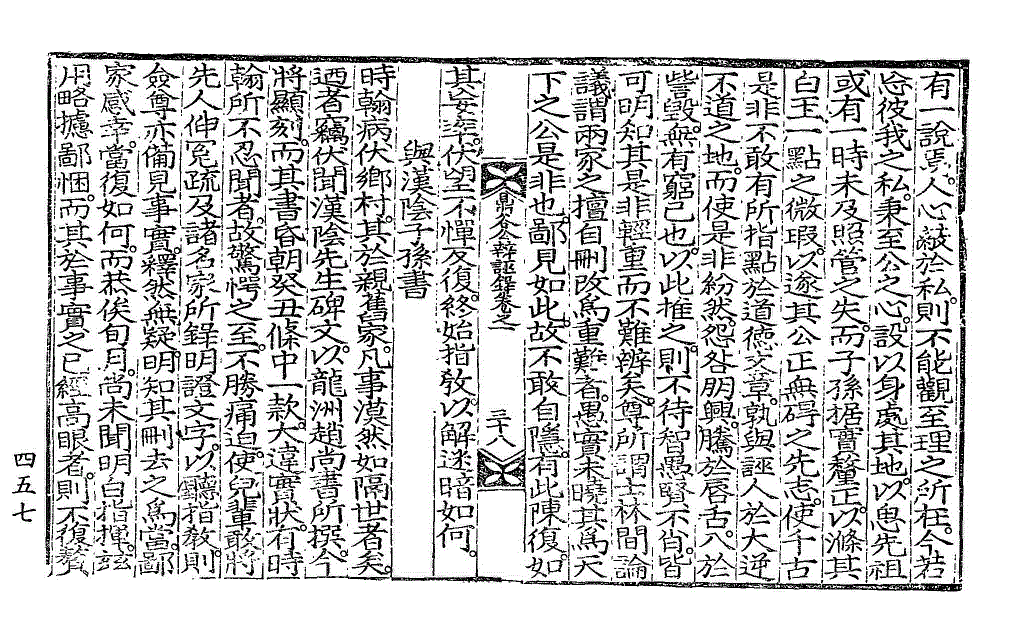 有一说焉。人心蔽于私。则不能观至理之所在。今若忘彼我之私。秉至公之心。设以身处其地。以思先祖或有一时未及照管之失。而子孙据实釐正。以涤其白玉一点之微瑕。以遂其公正无碍之先志。使千古是非不敢有所指点于道德文章。孰与诬人于大逆不道之地。而使是非纷然。怨咎朋兴。腾于唇舌。入于訾毁。无有穷已也。以此推之。则不待智愚贤不肖。皆可明知其是非轻重而不难辨矣。尊所谓士林间论议谓两家之擅自删改为重难者。愚实未晓其为天下之公是非也。鄙见如此。故不敢自隐。有此陈复。如其妄率。伏望不惮反复。终始指教。以解迷暗如何
有一说焉。人心蔽于私。则不能观至理之所在。今若忘彼我之私。秉至公之心。设以身处其地。以思先祖或有一时未及照管之失。而子孙据实釐正。以涤其白玉一点之微瑕。以遂其公正无碍之先志。使千古是非不敢有所指点于道德文章。孰与诬人于大逆不道之地。而使是非纷然。怨咎朋兴。腾于唇舌。入于訾毁。无有穷已也。以此推之。则不待智愚贤不肖。皆可明知其是非轻重而不难辨矣。尊所谓士林间论议谓两家之擅自删改为重难者。愚实未晓其为天下之公是非也。鄙见如此。故不敢自隐。有此陈复。如其妄率。伏望不惮反复。终始指教。以解迷暗如何与汉阴子孙书
时翰病伏乡村。其于亲旧家。凡事漠然如隔世者矣。乃者窃伏闻汉阴先生碑文。以龙洲赵尚书所撰。今将显刻。而其书昏朝癸丑条中一款。大违实状。有时翰所不忍闻者。故惊愕之至。不胜痛迫。使儿辈敢将先人伸冤疏及诸名家所录明證文字。以听指教。则佥尊亦备见事实。释然无疑。明知其删去之为当。鄙家感幸。当复如何。而恭俟旬月。尚未闻明白指挥。玆用略摅鄙悃。而其于事实之已经高眼者。则不复赘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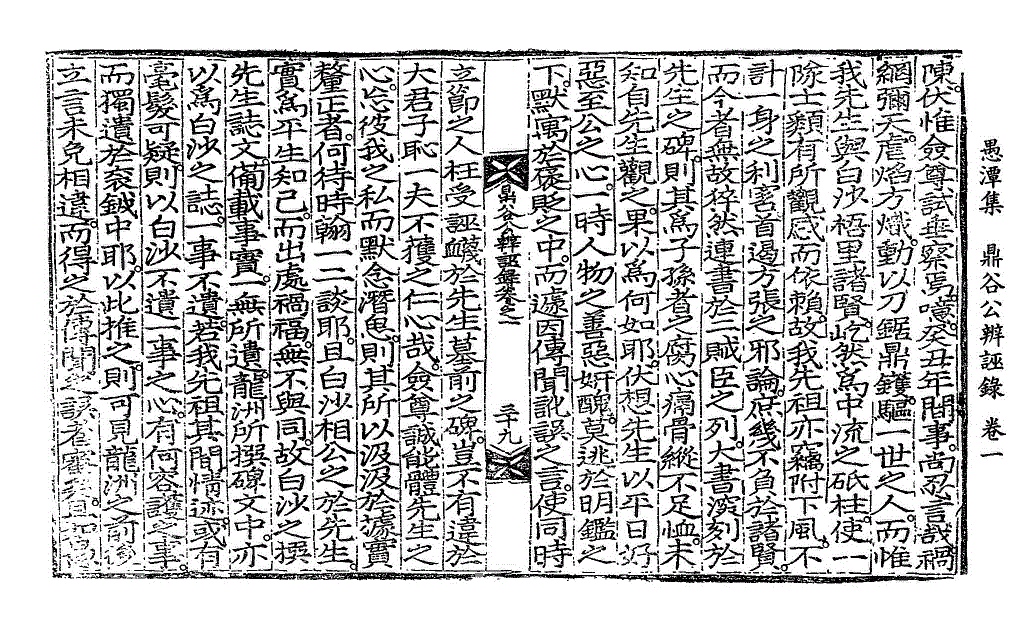 陈。伏惟佥尊试垂察焉。噫。癸丑年间事。尚忍言哉。祸网弥天。虐焰方炽。动以刀锯鼎镬。驱一世之人。而惟我先生与白沙,梧里诸贤。屹然为中流之砥柱。使一队士类有所观感而依赖。故我先祖亦窃附下风。不计一身之利害。首遏方张之邪论。庶几不负于诸贤。而今者无故猝然连书于二贼臣之列。大书深刻于先生之碑。则其为子孙者之腐心痛骨纵不足恤。未知自先生观之。果以为何如耶。伏想先生以平日好恶至公之心。一时人物之善恶妍丑。莫逃于明鉴之下。默寓于褒贬之中。而遽因传闻讹误之言。使同时立节之人枉受诬蔑于先生墓前之碑。岂不有违于大君子耻一夫不获之仁心哉。佥尊诚能体先生之心。忘彼我之私而默念潜思。则其所以汲汲于据实釐正者。何待时翰一二谈耶。且白沙相公之于先生。实为平生知己。而出处祸福。无不与同。故白沙之撰先生志文。备载事实。一无所遗。龙洲所撰碑文中。亦以为白沙之志。一事不遗。若我先祖其间情迹。或有毫发可疑。则以白沙不遗一事之心。有何容护之事。而独遗于衮钺中耶。以此推之。则可见龙洲之前后立言未免相违。而得之于传闻之误者审矣。且如愚
陈。伏惟佥尊试垂察焉。噫。癸丑年间事。尚忍言哉。祸网弥天。虐焰方炽。动以刀锯鼎镬。驱一世之人。而惟我先生与白沙,梧里诸贤。屹然为中流之砥柱。使一队士类有所观感而依赖。故我先祖亦窃附下风。不计一身之利害。首遏方张之邪论。庶几不负于诸贤。而今者无故猝然连书于二贼臣之列。大书深刻于先生之碑。则其为子孙者之腐心痛骨纵不足恤。未知自先生观之。果以为何如耶。伏想先生以平日好恶至公之心。一时人物之善恶妍丑。莫逃于明鉴之下。默寓于褒贬之中。而遽因传闻讹误之言。使同时立节之人枉受诬蔑于先生墓前之碑。岂不有违于大君子耻一夫不获之仁心哉。佥尊诚能体先生之心。忘彼我之私而默念潜思。则其所以汲汲于据实釐正者。何待时翰一二谈耶。且白沙相公之于先生。实为平生知己。而出处祸福。无不与同。故白沙之撰先生志文。备载事实。一无所遗。龙洲所撰碑文中。亦以为白沙之志。一事不遗。若我先祖其间情迹。或有毫发可疑。则以白沙不遗一事之心。有何容护之事。而独遗于衮钺中耶。以此推之。则可见龙洲之前后立言未免相违。而得之于传闻之误者审矣。且如愚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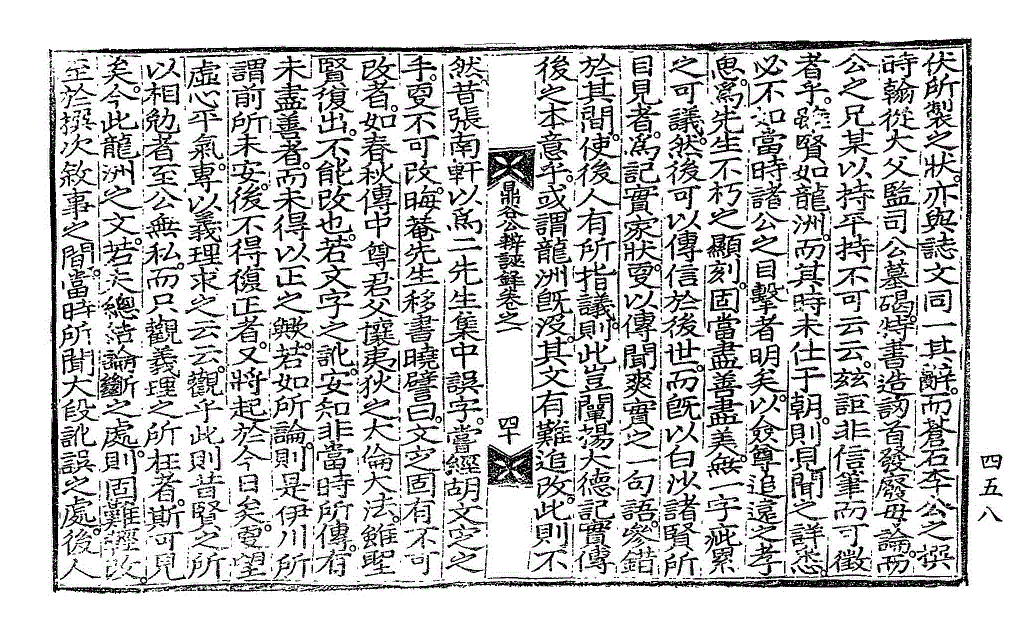 伏所制之状。亦与志文同一其辞。而苍石李公之撰时翰从大父监司公墓碣。特书造,讱首发废母论。而公之兄某以持平持不可云云。玆讵非信笔而可徵者乎。虽贤如龙洲。而其时未仕于朝。则见闻之详悉。必不如当时诸公之目击者明矣。以佥尊追远之孝思。为先生不朽之显刻。固当尽善尽美。无一字疵累之可议。然后可以传信于后世。而既以白沙诸贤所目见者。为记实家状。更以传闻爽实之一句语。参错于其间。使后人有所指议。则此岂阐扬大德记实传后之本意乎。或谓龙洲既没。其文有难追改。此则不然。昔张南轩以为二先生集中误字。尝经胡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晦庵先生移书晓譬曰。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春秋传中尊君父攘夷狄之大伦大法。虽圣贤复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讹。安知非当时所传。有未尽善者。而未得以正之欤。若如所论。则是伊川所谓前所未安。后不得复正者。又将起于今日矣。更望虚心平气。专以义理求之云云。观乎此则昔贤之所以相勉者至公无私。而只观义理之所在者。斯可见矣。今此龙洲之文。若夫总结论断之处。则固难轻改。至于撰次叙事之间。当时所闻大段讹误之处。后人
伏所制之状。亦与志文同一其辞。而苍石李公之撰时翰从大父监司公墓碣。特书造,讱首发废母论。而公之兄某以持平持不可云云。玆讵非信笔而可徵者乎。虽贤如龙洲。而其时未仕于朝。则见闻之详悉。必不如当时诸公之目击者明矣。以佥尊追远之孝思。为先生不朽之显刻。固当尽善尽美。无一字疵累之可议。然后可以传信于后世。而既以白沙诸贤所目见者。为记实家状。更以传闻爽实之一句语。参错于其间。使后人有所指议。则此岂阐扬大德记实传后之本意乎。或谓龙洲既没。其文有难追改。此则不然。昔张南轩以为二先生集中误字。尝经胡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晦庵先生移书晓譬曰。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春秋传中尊君父攘夷狄之大伦大法。虽圣贤复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讹。安知非当时所传。有未尽善者。而未得以正之欤。若如所论。则是伊川所谓前所未安。后不得复正者。又将起于今日矣。更望虚心平气。专以义理求之云云。观乎此则昔贤之所以相勉者至公无私。而只观义理之所在者。斯可见矣。今此龙洲之文。若夫总结论断之处。则固难轻改。至于撰次叙事之间。当时所闻大段讹误之处。后人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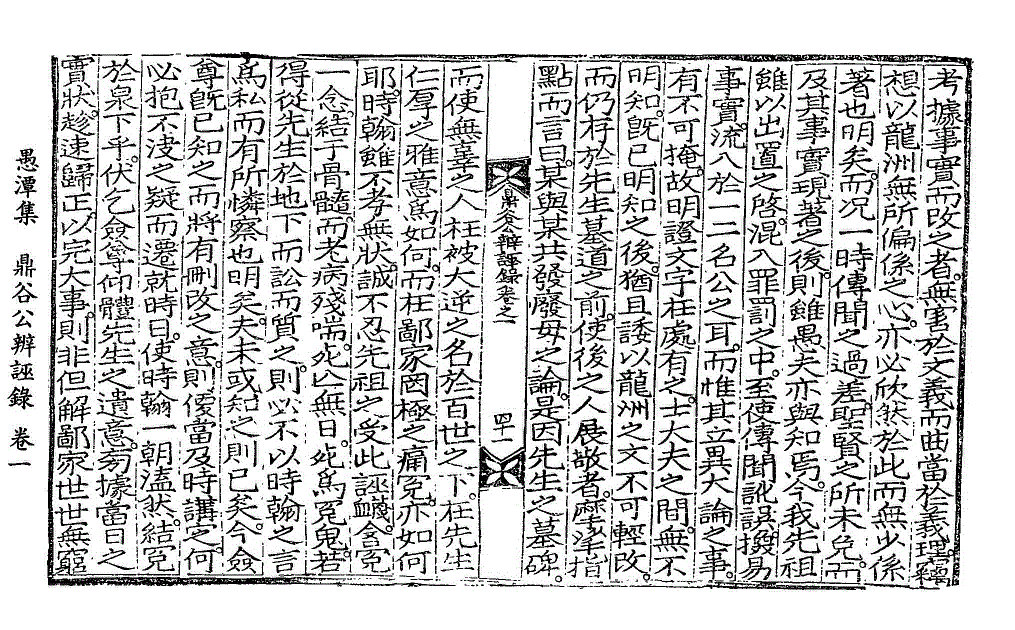 考据事实而改之者。无害于文义而曲当于义理。窃想以龙洲无所偏系之心。亦必欣然于此而无少系著也明矣。而况一时传闻之过差。圣贤之所未免。而及其事实现著之后。则虽愚夫亦与知焉。今我先祖虽以出置之启。混入罪罚之中。至使传闻讹误。换易事实。流入于一二名公之耳。而惟其立异大论之事。有不可掩。故明證文字在处有之。士大夫之间。无不明知。既已明知之后。犹且诿以龙洲之文不可轻改。而仍存于先生墓道之前。使后之人展敬者。摩挲指点而言曰。某与某共发废母之论。是因先生之墓碑。而使无辜之人枉被大逆之名于百世之下。在先生仁厚之雅意为如何。而在鄙家罔极之痛冤。亦如何耶。时翰虽不孝无状。诚不忍先祖之受此诬蔑。含冤一念。结于骨髓。而老病残喘。死亡无日。死为冤鬼。若得从先生于地下而讼而质之。则必不以时翰之言为私而有所怜察也明矣。夫未或知之则已矣。今佥尊既已知之而将有删改之意。则便当及时讲定。何必抱不决之疑而迁就时日。使时翰一朝溘然。结冤于泉下乎。伏乞佥尊仰体先生之遗意。旁据当日之实状。趁速归正。以完大事。则非但解鄙家世世无穷
考据事实而改之者。无害于文义而曲当于义理。窃想以龙洲无所偏系之心。亦必欣然于此而无少系著也明矣。而况一时传闻之过差。圣贤之所未免。而及其事实现著之后。则虽愚夫亦与知焉。今我先祖虽以出置之启。混入罪罚之中。至使传闻讹误。换易事实。流入于一二名公之耳。而惟其立异大论之事。有不可掩。故明證文字在处有之。士大夫之间。无不明知。既已明知之后。犹且诿以龙洲之文不可轻改。而仍存于先生墓道之前。使后之人展敬者。摩挲指点而言曰。某与某共发废母之论。是因先生之墓碑。而使无辜之人枉被大逆之名于百世之下。在先生仁厚之雅意为如何。而在鄙家罔极之痛冤。亦如何耶。时翰虽不孝无状。诚不忍先祖之受此诬蔑。含冤一念。结于骨髓。而老病残喘。死亡无日。死为冤鬼。若得从先生于地下而讼而质之。则必不以时翰之言为私而有所怜察也明矣。夫未或知之则已矣。今佥尊既已知之而将有删改之意。则便当及时讲定。何必抱不决之疑而迁就时日。使时翰一朝溘然。结冤于泉下乎。伏乞佥尊仰体先生之遗意。旁据当日之实状。趁速归正。以完大事。则非但解鄙家世世无穷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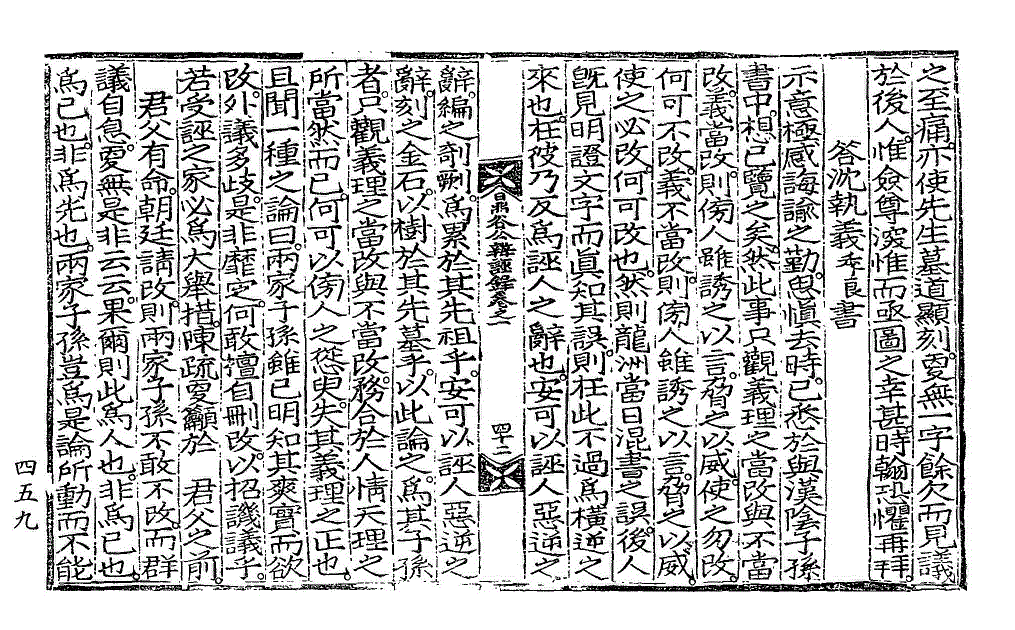 之至痛。亦使先生墓道显刻。更无一字馀欠而见议于后人。惟佥尊深惟而亟图之幸甚。时翰恐惧再拜。
之至痛。亦使先生墓道显刻。更无一字馀欠而见议于后人。惟佥尊深惟而亟图之幸甚。时翰恐惧再拜。答沈执义(季良)书
示意极感诲谕之勤。思慎去时。已悉于与汉阴子孙书中。想已览之矣。然此事只观义理之当改与不当改。义当改。则傍人虽诱之以言。胁之以威。使之勿改。何可不改。义不当改。则傍人虽诱之以言。胁之以威。使之必改。何可改也。然则龙洲当日混书之误。后人既见明證文字而真知其误。则在此不过为横逆之来也。在彼乃反为诬人之辞也。安可以诬人恶逆之辞。编之剞劂。为累于其先祖乎。安可以诬人恶逆之辞。刻之金石。以树于其先墓乎。以此论之。为其子孙者。只观义理之当改与不当改。务合于人情天理之所当然而已。何可以傍人之怂臾。失其义理之正也。且闻一种之论曰。两家子孙虽已明知其爽实而欲改。外议多岐。是非靡定。何敢擅自删改。以招讥议乎。若受诬之家必为大举措。陈疏更吁于 君父之前。 君父有命。朝廷请改。则两家子孙不敢不改。而群议自息。更无是非云云。果尔则此为人也。非为己也。为己也。非为先也。两家子孙岂为是论所动而不能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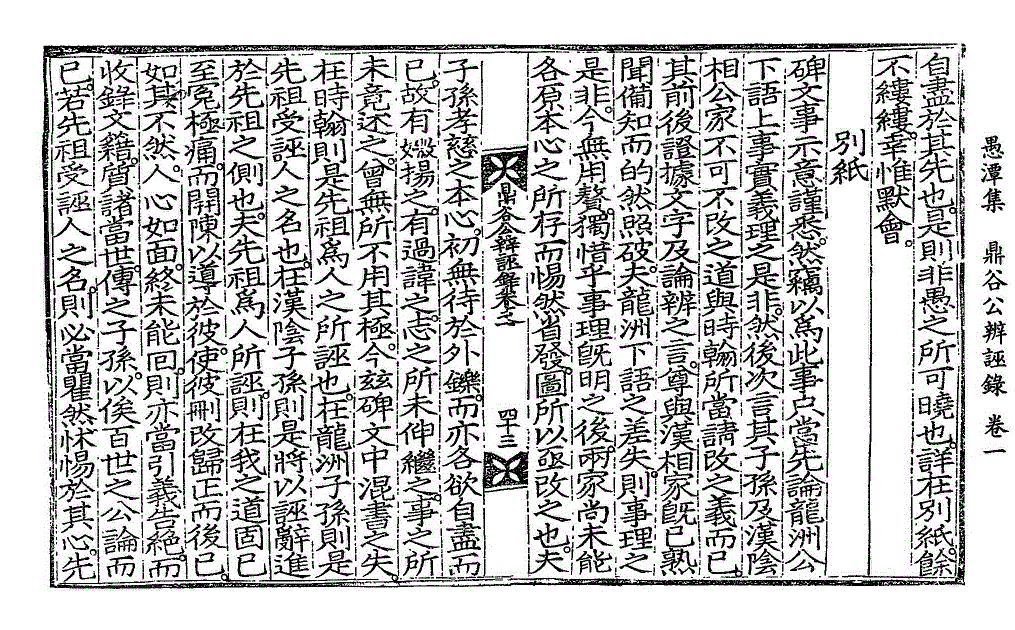 自尽于其先也。是则非愚之所可晓也。详在别纸。馀不缕缕。幸惟默会。
自尽于其先也。是则非愚之所可晓也。详在别纸。馀不缕缕。幸惟默会。别纸
碑文事示意谨悉。然窃以为此事只当先论龙洲公下语上事实义理之是非。然后次言其子孙及汉阴相公家不可不改之道与时翰所当请改之义而已。其前后證据文字及论辨之言。尊与汉相家既已熟闻备知而的然照破。夫龙洲下语之差失。则事理之是非。今无用赘。独惜乎事理既明之后。两家尚未能各原本心之所存而惕然省发。图所以亟改之也。夫子孙孝慈之本心。初无待于外铄。而亦各欲自尽而已。故有美扬之。有过讳之。志之所未伸继之。事之所未竟述之。曾无所不用其极。今玆碑文中混书之失。在时翰则是先祖为人之所诬也。在龙洲子孙则是先祖受诬人之名也。在汉阴子孙则是将以诬辞进于先祖之侧也。夫先祖为人所诬。则在我之道固已至冤极痛。而开陈以导于彼。使彼删改归正而后已。如其不然。人心如面。终未能回。则亦当引义告绝。而收录文籍。质诸当世。传之子孙。以俟百世之公论而已。若先祖受诬人之名。则必当瞿然怵惕于其心。先
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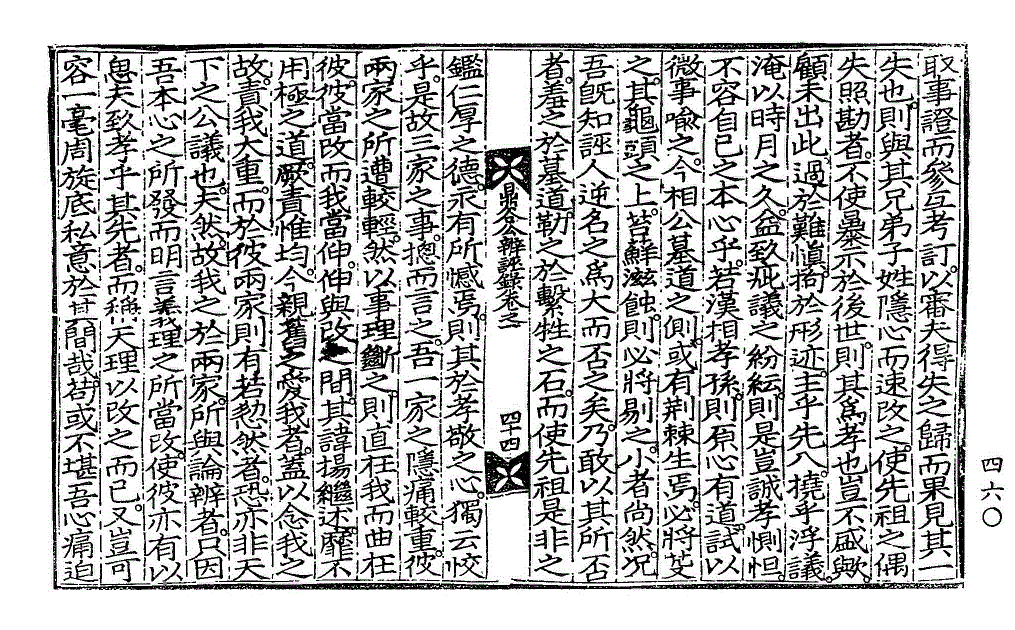 取事證而参互考订。以审夫得失之归而果见其一失也。则与其兄弟子姓隐心而速改之。使先祖之偶失照勘者。不使暴示于后世。则其为孝也岂不盛欤。顾未出此。过于难慎。拘于形迹。主乎先入。挠乎浮议。淹以时月之久。益致疵议之纷纭。则是岂诚孝恻怛。不容自己之本心乎。若汉相孝孙。则原心有道。试以微事喻之。今相公墓道之侧。或有荆棘生焉。必将芟之。其龟头之上。苔藓滋蚀。则必将剔之。小者尚然。况吾既知诬人逆名之为大而否之矣。乃敢以其所否者。羞之于墓道。勒之于系牲之石。而使先祖是非之鉴仁厚之德。永有所憾焉。则其于孝敬之心。独云恔乎。是故三家之事。总而言之。吾一家之隐痛较重。彼两家之所遭较轻。然以事理断之。则直在我而曲在彼。彼当改而我当伸。伸与改之间。其讳扬继述。靡不用极之道。厥责惟均。今亲旧之爱我者。盖以念我之故。责我大重。而于彼两家则有若恝然者。恐亦非天下之公议也。夫然。故我之于两家。所与论辨者。只因吾本心之所发而明言义理之所当改。使彼亦有以思夫致孝乎其先者。而称天理以改之而已。又岂可容一毫周旋底私意于其间哉。苟或不堪吾心痛迫
取事證而参互考订。以审夫得失之归而果见其一失也。则与其兄弟子姓隐心而速改之。使先祖之偶失照勘者。不使暴示于后世。则其为孝也岂不盛欤。顾未出此。过于难慎。拘于形迹。主乎先入。挠乎浮议。淹以时月之久。益致疵议之纷纭。则是岂诚孝恻怛。不容自己之本心乎。若汉相孝孙。则原心有道。试以微事喻之。今相公墓道之侧。或有荆棘生焉。必将芟之。其龟头之上。苔藓滋蚀。则必将剔之。小者尚然。况吾既知诬人逆名之为大而否之矣。乃敢以其所否者。羞之于墓道。勒之于系牲之石。而使先祖是非之鉴仁厚之德。永有所憾焉。则其于孝敬之心。独云恔乎。是故三家之事。总而言之。吾一家之隐痛较重。彼两家之所遭较轻。然以事理断之。则直在我而曲在彼。彼当改而我当伸。伸与改之间。其讳扬继述。靡不用极之道。厥责惟均。今亲旧之爱我者。盖以念我之故。责我大重。而于彼两家则有若恝然者。恐亦非天下之公议也。夫然。故我之于两家。所与论辨者。只因吾本心之所发而明言义理之所当改。使彼亦有以思夫致孝乎其先者。而称天理以改之而已。又岂可容一毫周旋底私意于其间哉。苟或不堪吾心痛迫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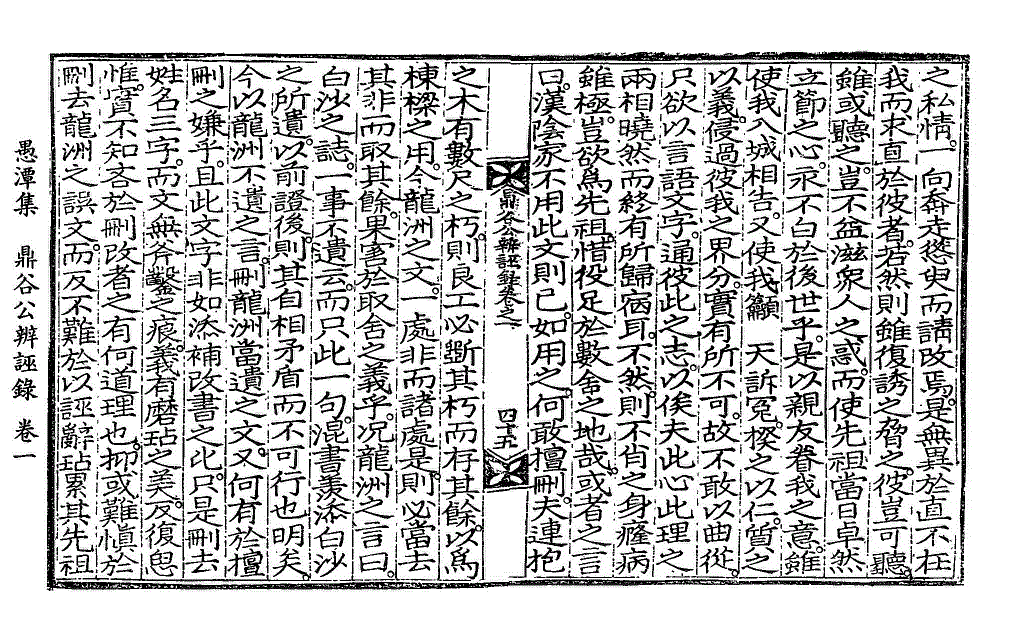 之私情。一向奔走怂臾而请改焉。是无异于直不在我而求直于彼者。若然则虽复诱之胁之。彼岂可听。虽或听之。岂不益滋众人之惑。而使先祖当日卓然立节之心。永不白于后世乎。是以亲友眷我之意。虽使我入城相告。又使我吁 天诉冤。揆之以仁。质之以义。侵过彼我之界分。实有所不可。故不敢以曲从。只欲以言语文字。通彼此之志。以俟夫此心此理之两相晓然而终有所归宿耳。不然。则不肖之身癃病虽极。岂欲为先祖。惜役足于数舍之地哉。或者之言曰。汉阴家不用此文则已。如用之。何敢擅删。夫连抱之木有数尺之朽。则良工必斲其朽而存其馀。以为栋梁之用。今龙洲之文。一处非而诸处是。则必当去其非而取其馀。果害于取舍之义乎。况龙洲之言曰。白沙之志。一事不遗云。而只此一句。混书羡添白沙之所遗。以前證后。则其自相矛盾而不可行也明矣。今以龙洲不遗之言。删龙洲当遗之文。又何有于擅删之嫌乎。且此文字非如添补改书之比。只是删去姓名三字。而文无斧凿之痕。义有磨玷之美。反复思惟。实不知吝于删改者之有何道理也。抑或难慎于删去龙洲之误文。而反不难于以诬辞玷累其先祖
之私情。一向奔走怂臾而请改焉。是无异于直不在我而求直于彼者。若然则虽复诱之胁之。彼岂可听。虽或听之。岂不益滋众人之惑。而使先祖当日卓然立节之心。永不白于后世乎。是以亲友眷我之意。虽使我入城相告。又使我吁 天诉冤。揆之以仁。质之以义。侵过彼我之界分。实有所不可。故不敢以曲从。只欲以言语文字。通彼此之志。以俟夫此心此理之两相晓然而终有所归宿耳。不然。则不肖之身癃病虽极。岂欲为先祖。惜役足于数舍之地哉。或者之言曰。汉阴家不用此文则已。如用之。何敢擅删。夫连抱之木有数尺之朽。则良工必斲其朽而存其馀。以为栋梁之用。今龙洲之文。一处非而诸处是。则必当去其非而取其馀。果害于取舍之义乎。况龙洲之言曰。白沙之志。一事不遗云。而只此一句。混书羡添白沙之所遗。以前證后。则其自相矛盾而不可行也明矣。今以龙洲不遗之言。删龙洲当遗之文。又何有于擅删之嫌乎。且此文字非如添补改书之比。只是删去姓名三字。而文无斧凿之痕。义有磨玷之美。反复思惟。实不知吝于删改者之有何道理也。抑或难慎于删去龙洲之误文。而反不难于以诬辞玷累其先祖鼎谷公辨诬录卷之一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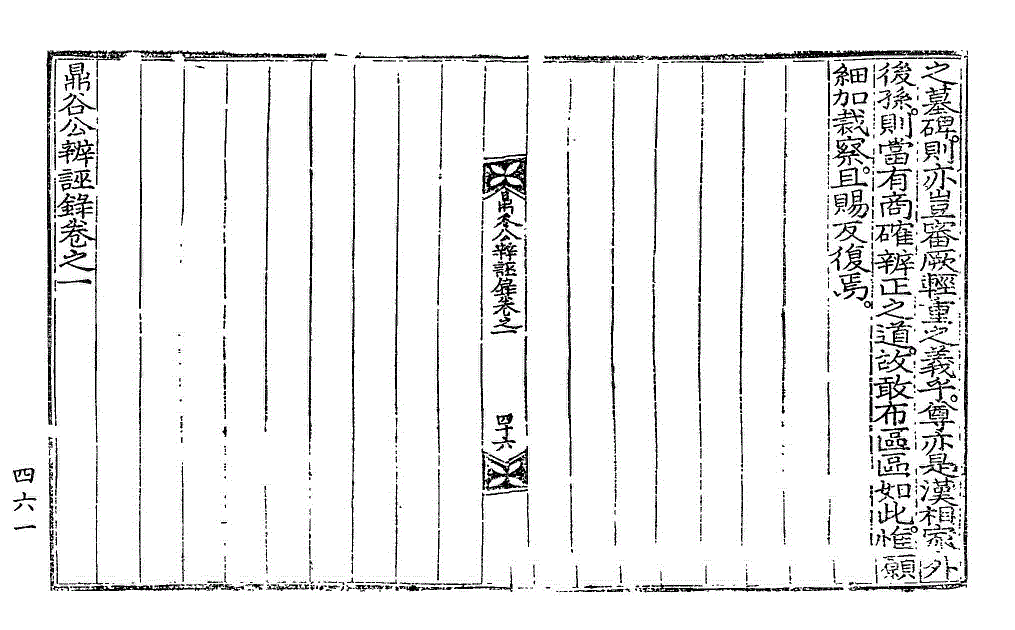 之墓碑。则亦岂审厥轻重之义乎。尊亦是汉相家外后孙。则当有商确辨正之道。故敢布区区如此。惟愿细加裁察。且赐反复焉。
之墓碑。则亦岂审厥轻重之义乎。尊亦是汉相家外后孙。则当有商确辨正之道。故敢布区区如此。惟愿细加裁察。且赐反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