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惕斋集卷之十 第 x 页
惕斋集卷之十
尚书讲义[一]
尚书讲义[一]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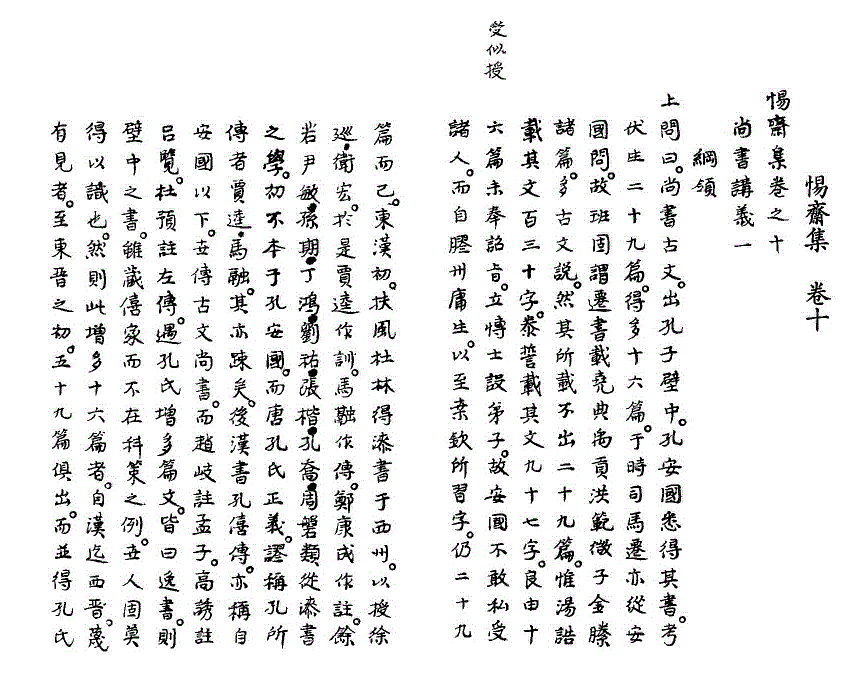 纲领
纲领上问曰。尚书古文。出孔子壁中。孔安国悉得其书。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于时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班固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然其所载不出二十九篇。惟汤诰载其文百三十字。泰誓载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诏旨。立博士设弟子。故安国不敢私受(受似授)诸人。而自胶州庸生。以至桑钦所习字。仍二十九篇而已。东汉初。扶风杜林得漆书于西州。以授徐巡,卫宏。于是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康成作注。馀若尹敏,孙期,丁鸿,刘祐,张楷,孔乔,周磐类从漆书之学。初不本于孔安国。而唐孔氏正义。谬称孔所传者贾逵,马融。其亦疏矣。后汉书孔僖传。亦称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而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览。杜预注左传。遇孔氏增多篇文。皆曰逸书。则壁中之书。虽藏僖家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得以识也。然则此增多十六篇者。自汉迄西晋。蔑有见者。至东晋之初。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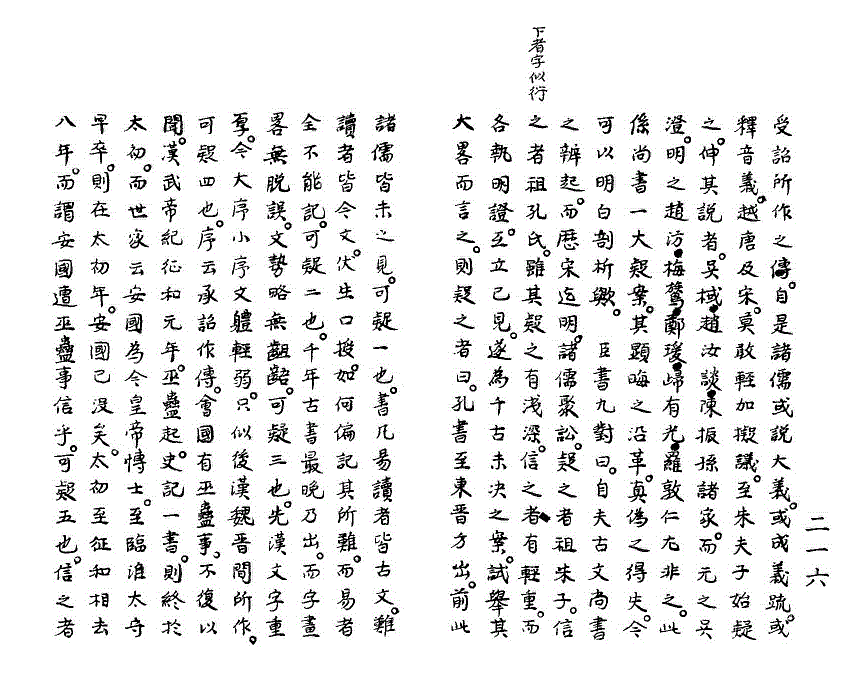 受诏所作之传。自是诸儒或说大义。或成义疏。或释音义。越唐及宋。莫敢轻加拟议。至朱夫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而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尤非之。此系尚书一大疑案。其显晦之沿革。真伪之得失。今可以明白剖析欤。
受诏所作之传。自是诸儒或说大义。或成义疏。或释音义。越唐及宋。莫敢轻加拟议。至朱夫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而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尤非之。此系尚书一大疑案。其显晦之沿革。真伪之得失。今可以明白剖析欤。臣书九对曰。自夫古文尚书之辨起。而历宋迄明。诸儒聚讼。疑之者祖朱子。信之者祖孔氏。虽其疑之有浅深。信之者(下者字似衍)有轻重。而各执明證。互立己见。遂为千古未决之案。试举其大略而言之。则疑之者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之见。可疑一也。书凡易读者皆古文。难读者皆今文。伏生口授。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可疑二也。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可疑三也。先汉文字重厚。今大序小序文体轻弱。只似后汉魏晋间所作。可疑四也。序云承诏作传。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汉武帝纪征和元年。巫蛊起。史记一书。则终于太初。而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安国已没矣。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而谓安国遭巫蛊事信乎。可疑五也。信之者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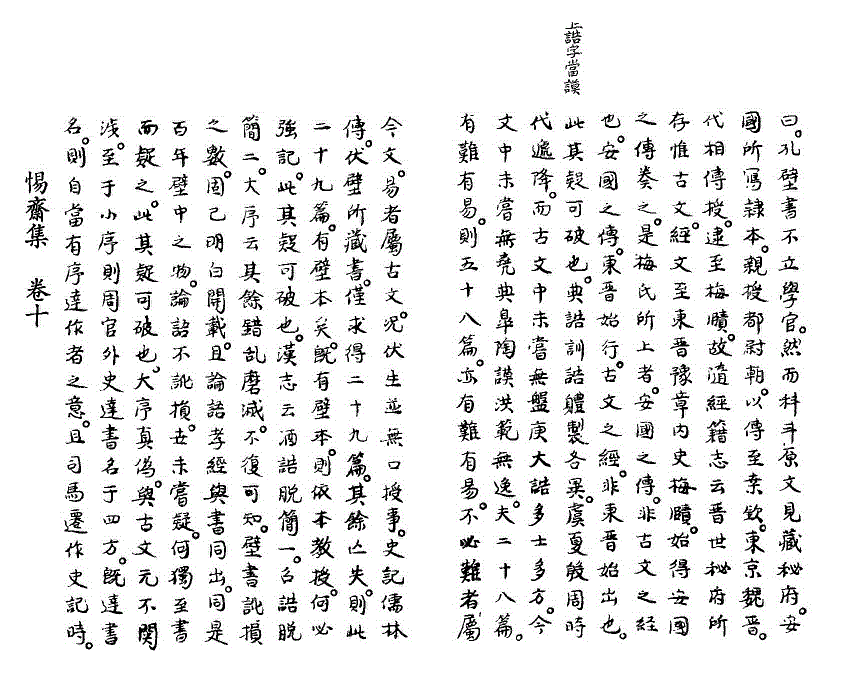 曰。孔壁书不立学官。然而科斗原文见藏秘府。安国所写隶本。亲授都尉朝。以传至桑钦。东京魏晋。代相传授。逮至梅赜。故随经籍志云晋世秘府所存惟古文。经文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是梅氏所上者。安国之传。非古文之经也。安国之传。东晋始行。古文之经。非东晋始出也。此其疑可破也。典谟训诰体制各异。虞夏殷周时代递降。而古文中未尝无盘庚大诰多士多方。今文中未尝无尧典皋陶谟洪范无逸。夫二十八篇。有难有易。则五十八篇。亦有难有易。不必难者属今文。易者属古文。况伏生并无口授事。史记儒林传。伏壁所藏书。仅求得二十九篇。其馀亡失。则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则依本教授。何必强记。此其疑可破也。汉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大序云其馀错乱磨灭。不复可知。壁书讹损之数。固已明白开载。且论语孝经与书同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论语不讹损。世未尝疑。何独至书而疑之。此其疑可破也。大序真伪。与古文元不关涉。至于小序则周官外史达书名于四方。既达书名。则自当有序达作者之意。且司马迁作史记时。
曰。孔壁书不立学官。然而科斗原文见藏秘府。安国所写隶本。亲授都尉朝。以传至桑钦。东京魏晋。代相传授。逮至梅赜。故随经籍志云晋世秘府所存惟古文。经文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是梅氏所上者。安国之传。非古文之经也。安国之传。东晋始行。古文之经。非东晋始出也。此其疑可破也。典谟训诰体制各异。虞夏殷周时代递降。而古文中未尝无盘庚大诰多士多方。今文中未尝无尧典皋陶谟洪范无逸。夫二十八篇。有难有易。则五十八篇。亦有难有易。不必难者属今文。易者属古文。况伏生并无口授事。史记儒林传。伏壁所藏书。仅求得二十九篇。其馀亡失。则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则依本教授。何必强记。此其疑可破也。汉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大序云其馀错乱磨灭。不复可知。壁书讹损之数。固已明白开载。且论语孝经与书同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论语不讹损。世未尝疑。何独至书而疑之。此其疑可破也。大序真伪。与古文元不关涉。至于小序则周官外史达书名于四方。既达书名。则自当有序达作者之意。且司马迁作史记时。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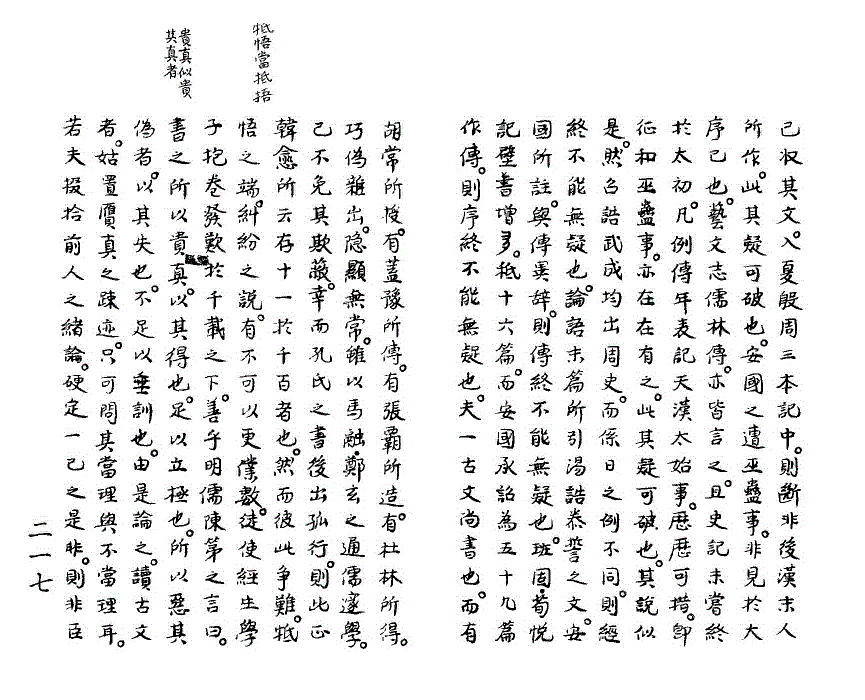 已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记中。则断非后汉末人所作。此其疑可破也。安国之遭巫蛊事。非见于大序已也。艺文志儒林传。亦皆言之。且史记未尝终于太初。凡例传年表记天汉太始事。历历可措。即征和巫蛊事。亦在在有之。此其疑可破也。其说似是。然召诰武成均出周史。而系日之例不同。则经终不能无疑也。论语末篇所引汤诰泰誓之文。安国所注。与传异辞。则传终不能无疑也。班固,荀悦记壁书增多。秪十六篇。而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则序终不能无疑也。夫一古文尚书也。而有胡常所授。有盖豫所传。有张霸所造。有杜林所得。巧伪杂出。隐显无常。虽以马融,郑玄之通儒邃学。已不免其欺蔽。幸而孔氏之书后出孤行。则此正韩愈所云存十一于千百者也。然而彼此争难。抵捂之端。纠纷之说。有不可以更仆数。徒使经生学子抱卷发叹于千载之下。善乎明儒陈第之言曰。书之所以贵真(贵真。似贵其真者。)。以其得也。足以立极也。所以恶其伪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训也。由是论之。读古文者。姑置赝真之疏迹。只可问其当理与不当理耳。若夫掇拾前人之绪论。硬定一己之是非。则非臣
已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记中。则断非后汉末人所作。此其疑可破也。安国之遭巫蛊事。非见于大序已也。艺文志儒林传。亦皆言之。且史记未尝终于太初。凡例传年表记天汉太始事。历历可措。即征和巫蛊事。亦在在有之。此其疑可破也。其说似是。然召诰武成均出周史。而系日之例不同。则经终不能无疑也。论语末篇所引汤诰泰誓之文。安国所注。与传异辞。则传终不能无疑也。班固,荀悦记壁书增多。秪十六篇。而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则序终不能无疑也。夫一古文尚书也。而有胡常所授。有盖豫所传。有张霸所造。有杜林所得。巧伪杂出。隐显无常。虽以马融,郑玄之通儒邃学。已不免其欺蔽。幸而孔氏之书后出孤行。则此正韩愈所云存十一于千百者也。然而彼此争难。抵捂之端。纠纷之说。有不可以更仆数。徒使经生学子抱卷发叹于千载之下。善乎明儒陈第之言曰。书之所以贵真(贵真。似贵其真者。)。以其得也。足以立极也。所以恶其伪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训也。由是论之。读古文者。姑置赝真之疏迹。只可问其当理与不当理耳。若夫掇拾前人之绪论。硬定一己之是非。则非臣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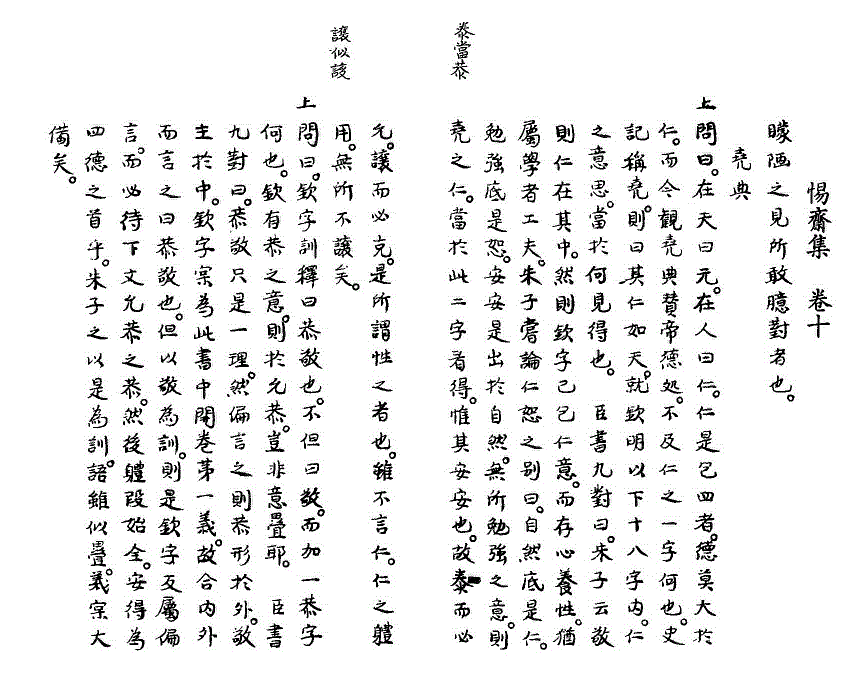 矇陋之见所敢臆对者也。
矇陋之见所敢臆对者也。尧典
上问曰。在天曰元。在人曰仁。仁是包四者。德莫大于仁。而今观尧典赞帝德处。不及仁之一字何也。史记称尧。则曰其仁如天。就钦明以下十八字内。仁之意思。当于何见得也。
臣书九对曰。朱子云敬则仁在其中。然则钦字已包仁意。而存心养性。犹属学者工夫。朱子尝论仁恕之别曰。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安安是出于自然。无所勉强之意。则尧之仁。当于此二字看得。惟其安安也。故恭而必允。让而必克。是所谓性之者也。虽不言仁。仁之体用。无所不让(让似该)矣。
上问曰。钦字训释曰恭敬也。不但曰敬。而加一恭字何也。钦有恭之意。则于允恭。岂非意叠耶。
臣书九对曰。恭敬只是一理。然偏言之则恭形于外。敬主于中。钦字宲为此书中开卷第一义。故合内外而言之曰恭敬也。但以敬为训。则是钦字反属偏言。而必待下文允恭之恭。然后体段始全。安得为四德之首乎。朱子之以是为训。语虽似叠。义宲大备矣。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8L 页
 上问曰。克明峻德。入于大学明明德传。而朱子曰。克明峻德。是明明德之意。峻德与明德。果无不同欤。大学之明明德。则明德本明。而为气拘欲蔽。有时而昏。故必下明之之工夫。而尧之峻德。则尧是性之者。峻德之光明自如。初无气拘欲蔽。有时而昏之事。则又安用明之之工夫。而曰克明峻德何也。克字有用力意。圣人之于德。亦必待用力修为而后明欤。
上问曰。克明峻德。入于大学明明德传。而朱子曰。克明峻德。是明明德之意。峻德与明德。果无不同欤。大学之明明德。则明德本明。而为气拘欲蔽。有时而昏。故必下明之之工夫。而尧之峻德。则尧是性之者。峻德之光明自如。初无气拘欲蔽。有时而昏之事。则又安用明之之工夫。而曰克明峻德何也。克字有用力意。圣人之于德。亦必待用力修为而后明欤。臣书九对曰。陈氏栎云明德。以此德本体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体之大言。所指各异。而峻德非有加于明德。其实则一也。人之为德。未尝不明。其明之为体。亦未尝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故必使明之。以复其初。惟圣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万善足焉。然朝乾夕惕。精一执中。使吾明德之全体大用。无有不明者。亦岂全无工夫。况不待修为而自明者。政见其己独能之。而人则不能。谓之克明峻德。不亦宜乎。
上问曰。九族有二义。一则集传说自高祖至玄孙之亲也。一则林少颖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集传不用林说。而其曰异姓之亲。亦在其中。又却似包得林说矣。亲之之道。固当及于异姓。然九族之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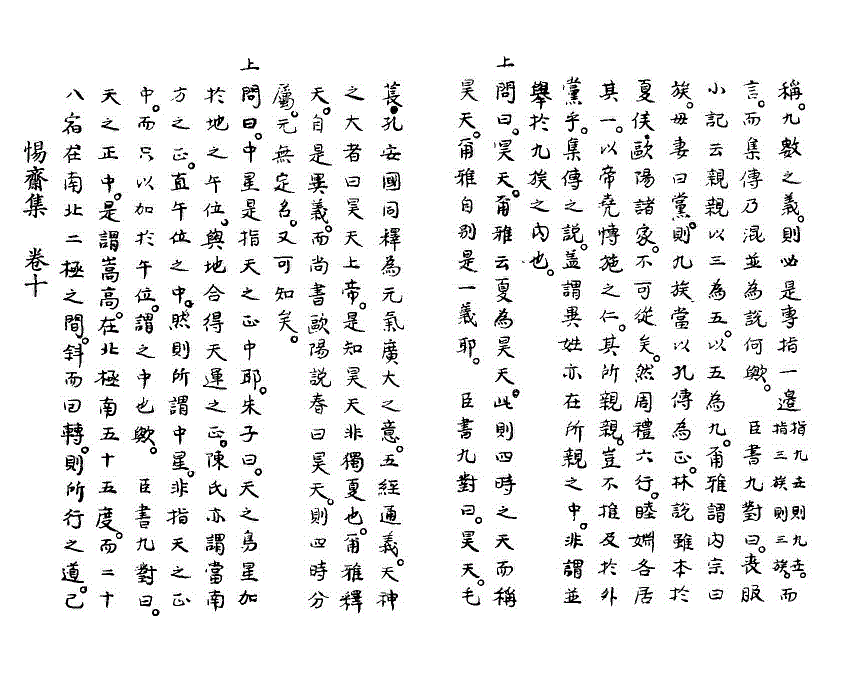 称。九数之义。则必是专指一边(指九世则九世。指三族则三族。)而言。而集传乃混并为说何欤。
称。九数之义。则必是专指一边(指九世则九世。指三族则三族。)而言。而集传乃混并为说何欤。臣书九对曰。丧服小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尔雅谓内宗曰族。母妻曰党。则九族当以孔传为正。林说虽本于夏侯,欧阳诸家。不可从矣。然周礼六行。睦姻各居其一。以帝尧博施之仁。其所亲亲。岂不推及于外党乎。集传之说。盖谓异姓亦在所亲之中。非谓并举于九族之内也。
上问曰。昊天。尔雅云夏为昊天。此则四时之天而称昊天。尔雅自别是一义耶。
臣书九对曰。昊天。毛苌,孔安国同释为元气广大之意。五经通义。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是知昊天非独夏也。尔雅释天。自是异义。而尚书欧阳说春曰昊天。则四时分属。元无定名。又可知矣。
上问曰。中星是指天之正中耶。朱子曰。天之鸟星加于地之午位。与地合得天运之正。陈氏亦谓当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然则所谓中星。非指天之正中。而只以加于午位。谓之中也欤。
臣书九对曰。天之正中。是谓嵩高。在北极南五十五度。而二十八宿在南北二极之间。斜而回转。则所行之道。已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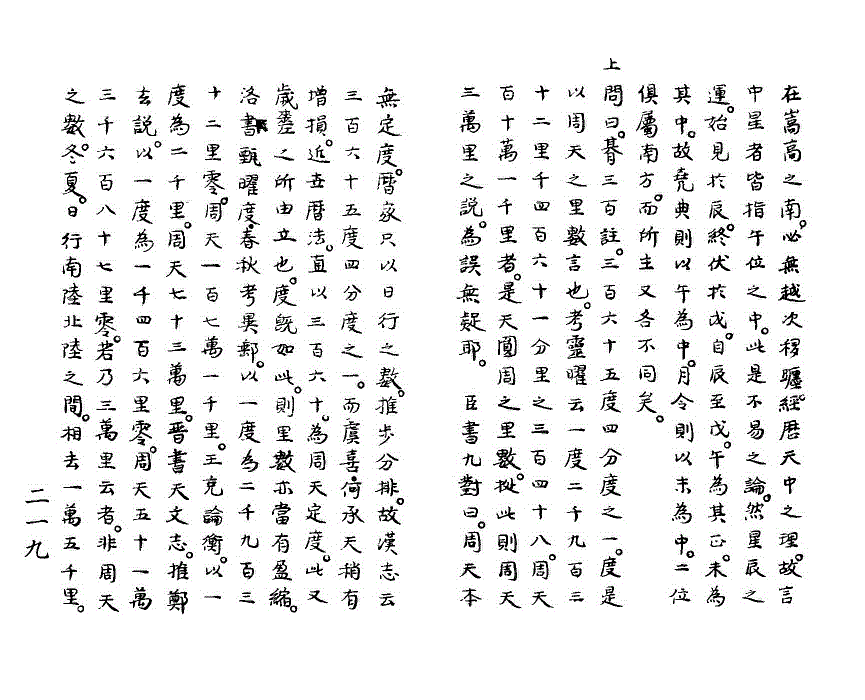 在嵩高之南。必无越次移躔。经历天中之理。故言中星者皆指午位之中。此是不易之论。然星辰之运。始见于辰。终伏于戌。自辰至戌。午为其正。未为其中。故尧典则以午为中。月令则以未为中。二位俱属南方。而所主又各不同矣。
在嵩高之南。必无越次移躔。经历天中之理。故言中星者皆指午位之中。此是不易之论。然星辰之运。始见于辰。终伏于戌。自辰至戌。午为其正。未为其中。故尧典则以午为中。月令则以未为中。二位俱属南方。而所主又各不同矣。上问曰。期三百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是以周天之里数言也。考灵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十万一千里者。是天圆周之里数。据此则周天三万里之说。为误无疑耶。
臣书九对曰。周天本无定度。历家只以日行之数。推步分排。故汉志云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虞喜,何承天稍有增损。近世历法。直以三百六十。为周天定度。此又岁𢀩之所由立也。度既如此。则里数亦当有盈缩。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以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零。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王充论衡。以一度为二千里。周天七十三万里。晋书天文志。推郑玄说。以一度为一千四百六里零。周天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零。若乃三万里云者。非周天之数。冬夏。日行南陆北陆之间。相去一万五千里。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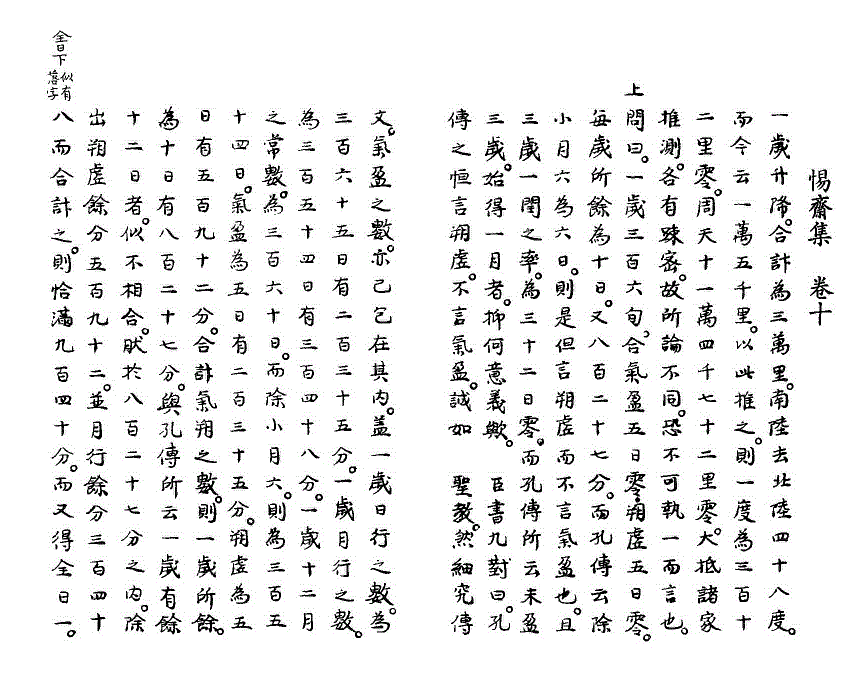 一岁升降。合计为三万里。南陆去北陆四十八度。而今云一万五千里。以此推之。则一度为三百十二里零。周天十一万四千七十二里零。大抵诸家推测。各有疏密。故所论不同。恐不可执一而言也。
一岁升降。合计为三万里。南陆去北陆四十八度。而今云一万五千里。以此推之。则一度为三百十二里零。周天十一万四千七十二里零。大抵诸家推测。各有疏密。故所论不同。恐不可执一而言也。上问曰。一岁三百六旬。合气盈五日零,朔虚五日零。每岁所馀为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而孔传云除小月六为六日。则是但言朔虚而不言气盈也。且三岁一闰之率。为三十二日零。而孔传所云未盈三岁。始得一月者。抑何意义欤。
臣书九对曰。孔传之恒言朔虚。不言气盈。诚如 圣教。然细究传文。气盈之数。亦已包在其内。盖一岁日行之数。为三百六十五日有二百三十五分。一岁月行之数。为三百五十四日有三百四十八分。一岁十二月之常数。为三百六十日。而除小月六。则为三百五十四日。气盈为五日有二百三十五分。朔虚为五日有五百九十二分。合计气朔之数。则一岁所馀。为十日有八百二十七分。与孔传所云一岁有馀十二日者。似不相合。肰于八百二十七分之内。除出朔虚馀分五百九十二。并月行馀分三百四十八而合计之。则恰满九百四十分。而又得全日(全日下似有落字)一。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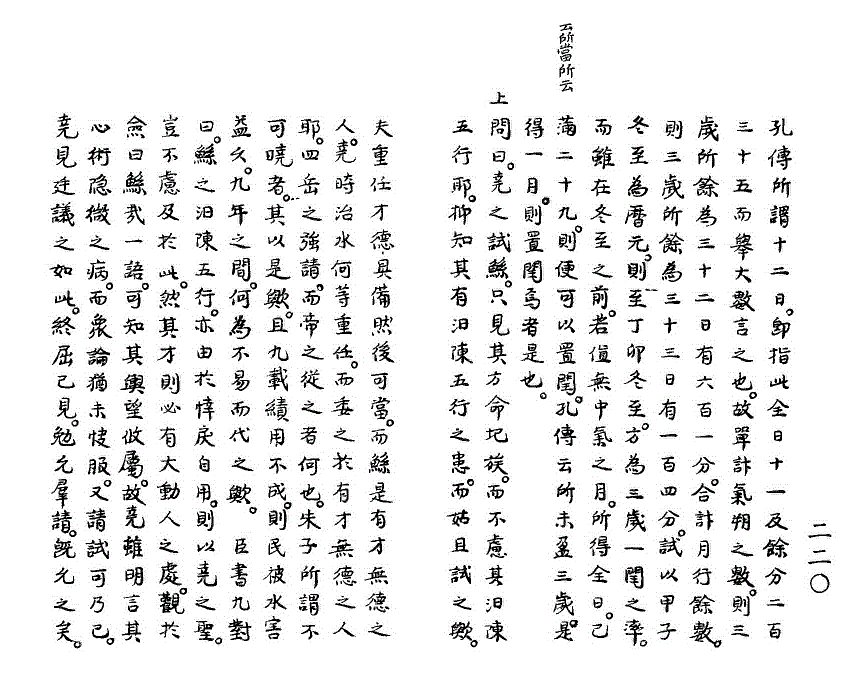 孔传所谓十二日。即指此全日十一及馀分二百三十五而举大数言之也。故单计气朔之数。则三岁所馀为三十二日有六百一分。合计月行馀数。则三岁所馀为三十三日有一百四分。试以甲子冬至为历元。则至丁卯冬至。方为三岁一闰之率。而虽在冬至之前。若值无中气之月。所得全日。已满二十九。则便可以置闰。孔传所云未盈三岁。是得一月。则置闰焉者是也。
孔传所谓十二日。即指此全日十一及馀分二百三十五而举大数言之也。故单计气朔之数。则三岁所馀为三十二日有六百一分。合计月行馀数。则三岁所馀为三十三日有一百四分。试以甲子冬至为历元。则至丁卯冬至。方为三岁一闰之率。而虽在冬至之前。若值无中气之月。所得全日。已满二十九。则便可以置闰。孔传所云未盈三岁。是得一月。则置闰焉者是也。上问曰。尧之试鲧。只见其方命圮族。而不虑其汩陈五行耶。抑知其有汩陈五行之患。而姑且试之欤。夫重任才德具备然后可当。而鲧是有才无德之人。尧时治水何等重任。而委之于有才无德之人耶。四岳之强请。而帝之从之者何也。朱子所谓不可晓者。其以是欤。且九载绩用不成。则民被水害益久。九年之间。何为不易而代之欤。
臣书九对曰。鲧之汩陈五行。亦由于悻戾自用。则以尧之圣。岂不虑及于此。然其才则必有大动人之处。观于佥曰鲧哉一语。可知其舆望攸属。故尧虽明言其心术隐微之病。而众论犹未快服。又请试可乃已。尧见廷议之如此。终屈己见。勉允群请。既允之矣。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1H 页
 又当久任而责成。故隐忍迟待。以讫三考。断知其绩用不成。然后始乃黜之。圣王用人之际。博询公议。不求近功之盛德至意。此可见矣。苏辙曰。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不仁则尧必不居。而方割之民。不忍坐视。佥同之谋。不当力拒。则尧之不知。不亦宜乎。及夫其言之不幸得中。则是终不失为知人之智也。
又当久任而责成。故隐忍迟待。以讫三考。断知其绩用不成。然后始乃黜之。圣王用人之际。博询公议。不求近功之盛德至意。此可见矣。苏辙曰。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不仁则尧必不居。而方割之民。不忍坐视。佥同之谋。不当力拒。则尧之不知。不亦宜乎。及夫其言之不幸得中。则是终不失为知人之智也。李秉模问曰。敬致之致。集传则作致日之致。而谓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识其景。史记孔安国注。则作致功之致。而谓以平秩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孔说较顺。而集传之不取何欤。若曰春秋皆有宾日饯日之礼。于夏不可独无云尔。则周礼冬夏。俱言致日。而此于幽都。无致日之礼者何欤。
书九曰。孔传之释敬致。谓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夫如是则羲和分命。莫不皆然。何独于南讹而言之。安国亦自知其义之未该。故乃曰四时同之。亦举一喁(喁似隅)。然则经文当系之于东作之下。以示春统四时之义。尤不当言之于仲夏。而周礼冬夏致日。既有明文。故集传不取孔说。但周礼并举冬夏。而此于幽都无致日之礼者。北方不见日。夏至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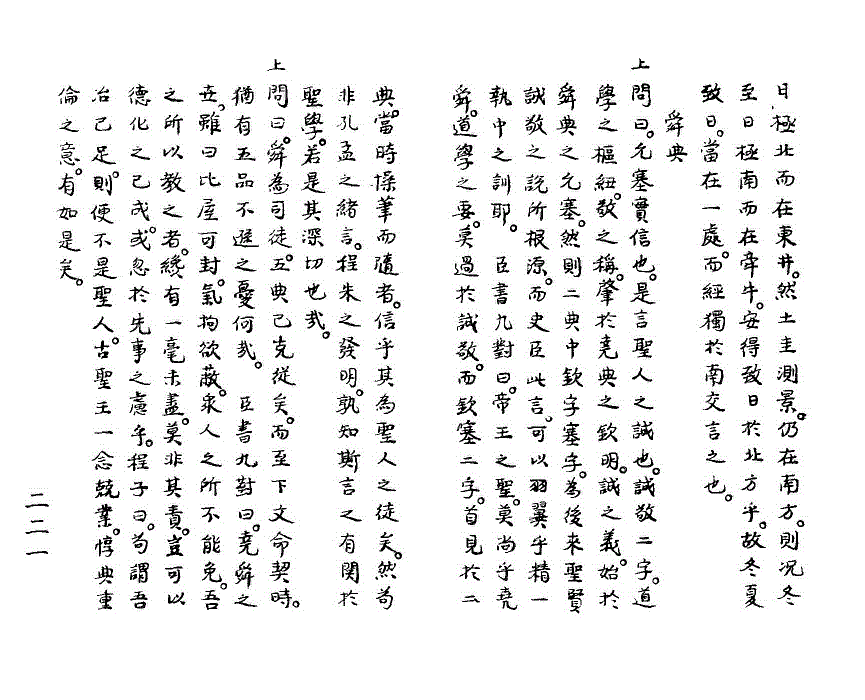 日极北而在东井。然土圭测景。仍在南方。则况冬至日极南而在牵牛。安得致日于北方乎。故冬夏致日。当在一处。而经独于南交言之也。
日极北而在东井。然土圭测景。仍在南方。则况冬至日极南而在牵牛。安得致日于北方乎。故冬夏致日。当在一处。而经独于南交言之也。舜典
上问曰。允塞实信也。是言圣人之诚也。诚敬二字。道学之枢纽。敬之称。肇于尧典之钦明。诚之义。始于舜典之允塞。然则二典中钦字塞字。为后来圣贤诚敬之说所根源。而史臣此言。可以羽翼乎精一执中之训耶。
臣书九对曰。帝王之圣。莫尚乎尧舜。道学之要。莫过于诚敬。而钦塞二字。首见于二典。当时操笔而随者。信乎其为圣人之徒矣。然苟非孔孟之绪言。程朱之发明。孰知斯言之有关于圣学。若是其深切也哉。
上问曰。舜为司徒。五典已克从矣。而至下文命契时。犹有五品不逊之忧何哉。
臣书九对曰。尧舜之世。虽曰比屋可封。气拘欲蔽。众人之所不能免。吾之所以教之者。才有一毫未尽。莫非其责。岂可以德化之已成。或忽于先事之虑乎。程子曰。苟谓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古圣王一念兢业。惇典重伦之意。有如是矣。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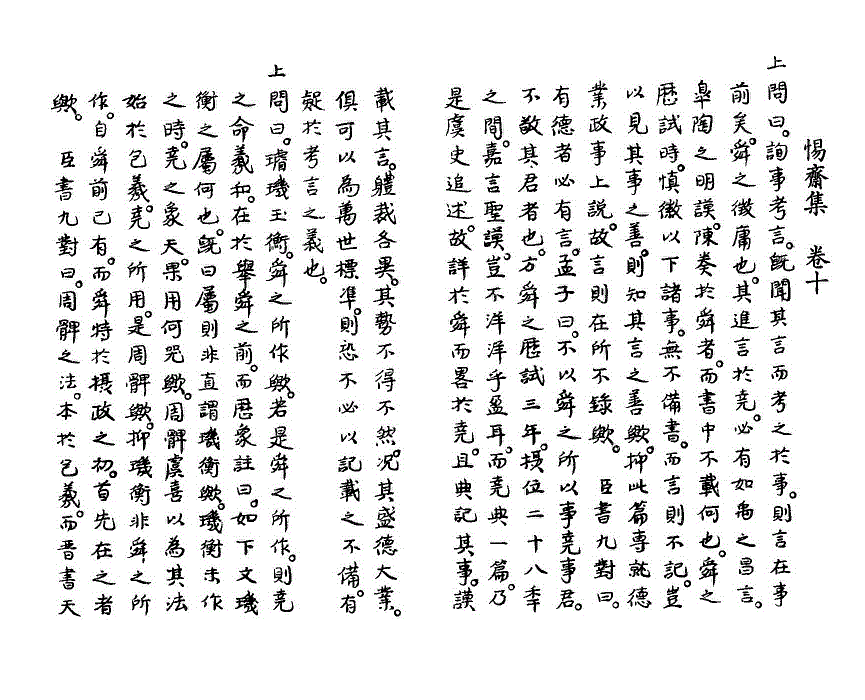 上问曰。询事考言。既闻其言而考之于事。则言在事前矣。舜之徵庸也。其进言于尧。必有如禹之昌言。皋陶之明谟。陈奏于舜者。而书中不载何也。舜之历试时。慎徽以下诸事。无不备书。而言则不记。岂以见其事之善。则知其言之善欤。抑此篇专就德业政事上说。故言则在所不录欤。
上问曰。询事考言。既闻其言而考之于事。则言在事前矣。舜之徵庸也。其进言于尧。必有如禹之昌言。皋陶之明谟。陈奏于舜者。而书中不载何也。舜之历试时。慎徽以下诸事。无不备书。而言则不记。岂以见其事之善。则知其言之善欤。抑此篇专就德业政事上说。故言则在所不录欤。臣书九对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方舜之历试三年。摄位二十八年之间。嘉言圣谟。岂不洋洋乎盈耳。而尧典一篇。乃是虞史追述。故详于舜而略于尧。且典记其事。谟载其言。体裁各异。其势不得不然。况其盛德大业。俱可以为万世标准。则恐不必以记载之不备。有疑于考言之义也。
上问曰。璿玑玉衡。舜之所作欤。若是舜之所作。则尧之命羲和。在于举舜之前。而历象注曰。如下文玑衡之属何也。既曰属则非直谓玑衡欤。玑衡未作之时。尧之象天。果用何器欤。周髀虞喜以为其法始于包羲。尧之所用。是周髀欤。抑玑衡非舜之所作。自舜前已有。而舜特于摄政之初。首先在之者欤。
臣书九对曰。周髀之法。本于包羲。而晋书天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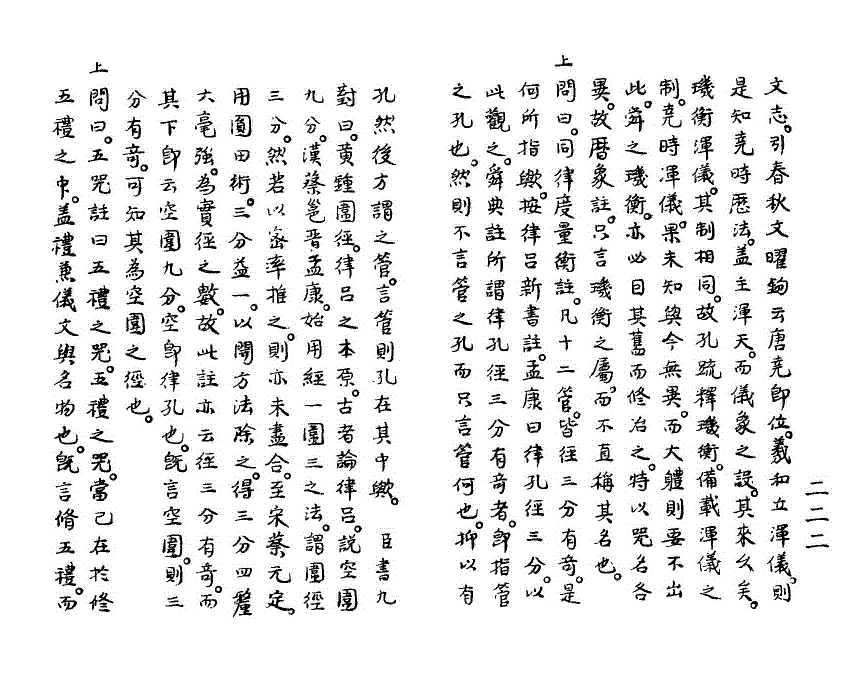 文志。引春秋文曜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则是知尧时历法。盖主浑天。而仪象之设。其来久矣。玑衡浑仪。其制相同。故孔疏释玑衡。备载浑仪之制。尧时浑仪。果未知与今无异。而大体则要不出此。舜之玑衡。亦必因其旧而修冶之。特以器名各异。故历象注。只言玑衡之属。而不直称其名也。
文志。引春秋文曜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则是知尧时历法。盖主浑天。而仪象之设。其来久矣。玑衡浑仪。其制相同。故孔疏释玑衡。备载浑仪之制。尧时浑仪。果未知与今无异。而大体则要不出此。舜之玑衡。亦必因其旧而修冶之。特以器名各异。故历象注。只言玑衡之属。而不直称其名也。上问曰。同律度量衡注。凡十二管。皆径三分有奇。是何所指欤。按律吕新书注。孟康曰律孔径三分。以此观之。舜典注所谓律孔径三分有奇者。即指管之孔也。然则不言管之孔而只言管何也。抑以有孔然后方谓之管。言管则孔在其中欤。
臣书九对曰。黄钟围径。律吕之本原。古者论律吕。说空围九分。汉蔡邕晋孟康。始用经一围三之法。谓围径三分。然若以密率推之。则亦未尽合。至宋蔡元定。用圆田术。三分益一。以开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强。为实径之数。故此注亦云径三分有奇。而其下即云空围九分。空即律孔也。既言空围。则三分有奇。可知其为空围之径也。
上问曰。五器注曰五礼之器。五礼之器。当已在于修五礼之中。盖礼兼仪文与名物也。既言脩五礼。而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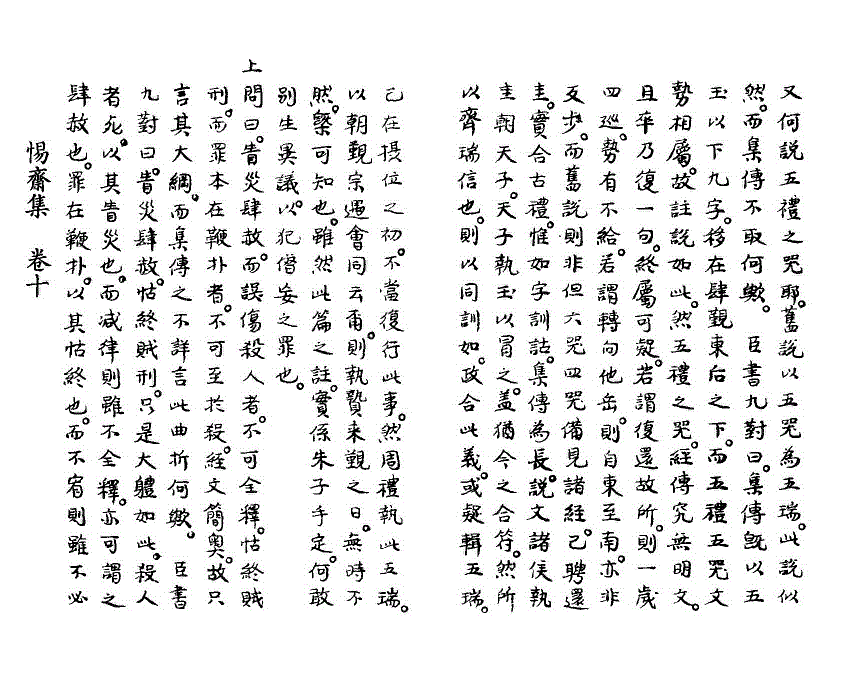 又何说五礼之器耶。旧说以五器为五瑞。此说似然。而集传不取何欤。
又何说五礼之器耶。旧说以五器为五瑞。此说似然。而集传不取何欤。臣书九对曰。集传既以五玉以下九字。移在肆觐东后之下。而五礼五器文势相属。故注说如此。然五礼之器。经传究无明文。且卒乃复一句。终属可疑。若谓复还故所。则一岁四巡。势有不给。若谓转向他岳。则自东至南。亦非反步。而旧说则非但六器四器备见诸经。已聘还圭。实合古礼。惟如字训诂。集传为长。说文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盖犹今之合符。然所以齐瑞信也。则以同训如。政合此义。或疑辑五瑞。已在摄位之初。不当复行此事。然周礼执此五瑞。以朝觐宗遇会同云尔。则执贽来觐之日。无时不然。槩可知也。虽然此篇之注。实系朱子手定。何敢别生异议。以犯僭妄之罪也。
上问曰。眚灾肆赦。而误伤杀人者。不可全释。怙终贼刑。而罪本在鞭扑者。不可至于杀。经文简奥。故只言其大纲。而集传之不详言此曲折何欤。
臣书九对曰。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只是大体如此。杀人者死。以其眚灾也。而减律则虽不全释。亦可谓之肆赦也。罪在鞭扑。以其怙终也。而不宥则虽不必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3L 页
 杀。亦可谓之贼刑也。其轻其重。惟在圣王原情定罪而已。集传所云法外意者。可谓言简而旨要矣。
杀。亦可谓之贼刑也。其轻其重。惟在圣王原情定罪而已。集传所云法外意者。可谓言简而旨要矣。上问曰。格于文祖。以即位告也。告即位与告摄一也。格文祖之下。又当有类禋望遍群神之节。而此不言者。欲与上文通看而不复举耶。
臣书九对曰。即位视摄位。其事尤重。然以常变言之。则即位是常礼。摄位是变礼。类禋望遍。天子事也。而舜已行之于摄位之初。故史皆谨书。至于即位之后。则自是天子应行之礼。故略而不书也。
上问曰。夙夜惟寅之寅。即寅宾寅饯之寅。而寅宾注曰寅敬也。惟寅注曰寅敬畏也。加一畏字。是盖注释愈详密而然欤。抑别有意义欤。或曰。此时言祭祀时。敬谓明神可畏也。是恐不然。敬本有戒慎恐惧之意。故朱子尝言敬惟畏字为近之。君子居敬。平日常若对越上帝。独于祭祀时畏神明耶。
臣书九对曰。寅宾之寅。不过是临事敬谨之意。惟寅之寅。乃是对越上帝。不显亦临之意。均是敬也。其体段之大小不同。故注释自有详略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君子居敬。岂容一息之间断。此虽主祭祀说。观于夙夜二字。可知其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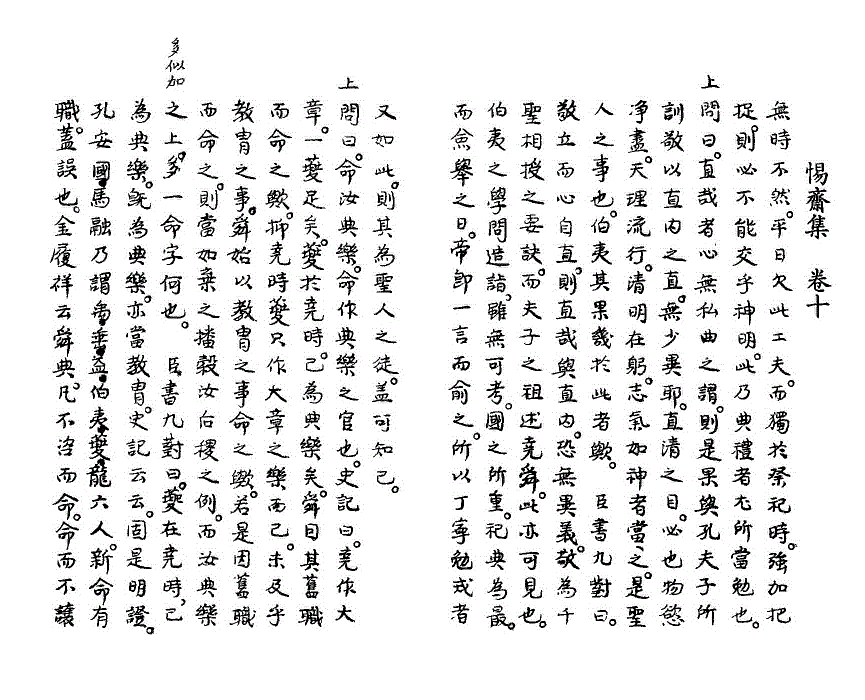 无时不然。平日欠此工夫。而独于祭祀时。强加把捉。则必不能交乎神明。此乃典礼者尤所当勉也。
无时不然。平日欠此工夫。而独于祭祀时。强加把捉。则必不能交乎神明。此乃典礼者尤所当勉也。上问曰。直哉者心无私曲之谓。则是果与孔夫子所训敬以直内之直。无少异耶。直清之目。必也物欲净尽。天理流行。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者当之。是圣人之事也。伯夷其果几于此者欤。
臣书九对曰。敬立而心自直。则直哉与直内。恐无异义。敬为千圣相授之要诀。而夫子之祖述尧舜。此亦可见也。伯夷之学问造诣。虽无可考。国之所重。祀典为最。而佥举之日。帝即一言而俞之。所以丁宁勉戒者又如此。则其为圣人之徒。盖可知已。
上问曰。命汝典乐。命作典乐之官也。史记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夔于尧时。已为典乐矣。舜因其旧职而命之欤。抑尧时夔只作大章之乐而已。未及乎教胄之事。舜始以教胄之事命之欤。若是因旧职而命之。则当如弃之播谷汝后稷之例。而汝典乐之上。多(多似加)一命字何也。
臣书九对曰。夔在尧时。已为典乐。既为典乐。亦当教胄。史记云云。固是明證。孔安国,马融乃谓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新命有职。盖误也。金履祥云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让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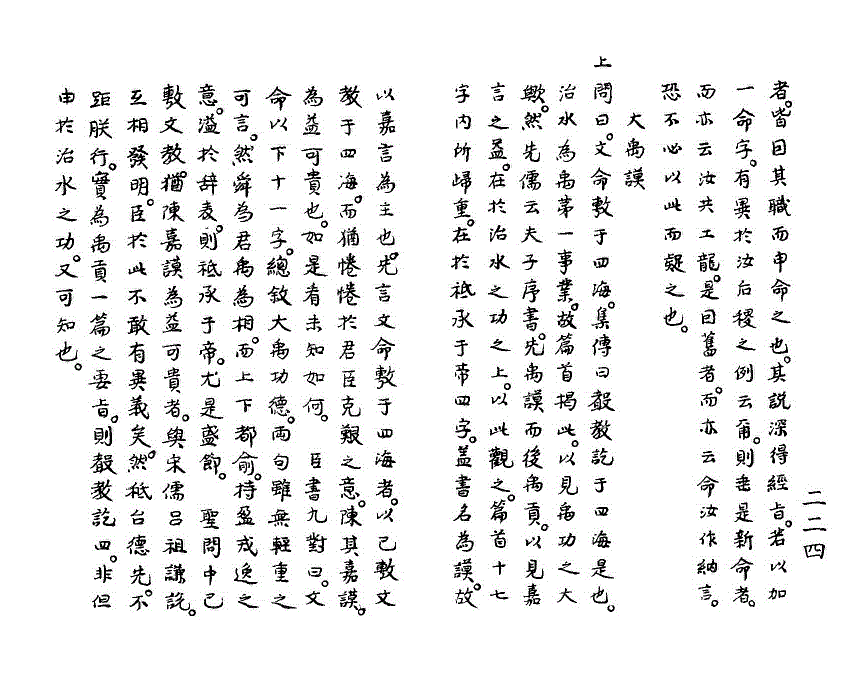 者。皆因其职而申命之也。其说深得经旨。若以加一命字。有异于汝后稷之例云尔。则垂是新命者。而亦云汝共工龙。是因旧者。而亦云命汝作纳言。恐不必以此而疑之也。
者。皆因其职而申命之也。其说深得经旨。若以加一命字。有异于汝后稷之例云尔。则垂是新命者。而亦云汝共工龙。是因旧者。而亦云命汝作纳言。恐不必以此而疑之也。大禹谟
上问曰。文命敷于四海。集传曰声教讫于四海是也。治水为禹第一事业。故篇首揭此。以见禹功之大欤。然先儒云夫子序书。先禹谟而后禹贡。以见嘉言之益。在于治水之功之上。以此观之。篇首十七字内所归重。在于祗承于帝四字。盖书名为谟。故以嘉言为主也。先言文命敷于四海者。以已敷文教于四海。而犹惓惓于君臣克艰之意。陈其嘉谟。为益可贵也。如是看未知如何。
臣书九对曰。文命以下十一字。总叙大禹功德。两句虽无轻重之可言。然舜为君禹为相。而上下都俞。持盈戒逸之意。溢于辞表。则祗承于帝。尤是盛节。 圣问中已敷文教。犹陈嘉谟为益可贵者。与宋儒吕祖谦说。互相发明。臣于此不敢有异义矣。然秪台德先。不距朕行。实为禹贡一篇之要旨。则声教讫四。非但由于治水之功。又可知也。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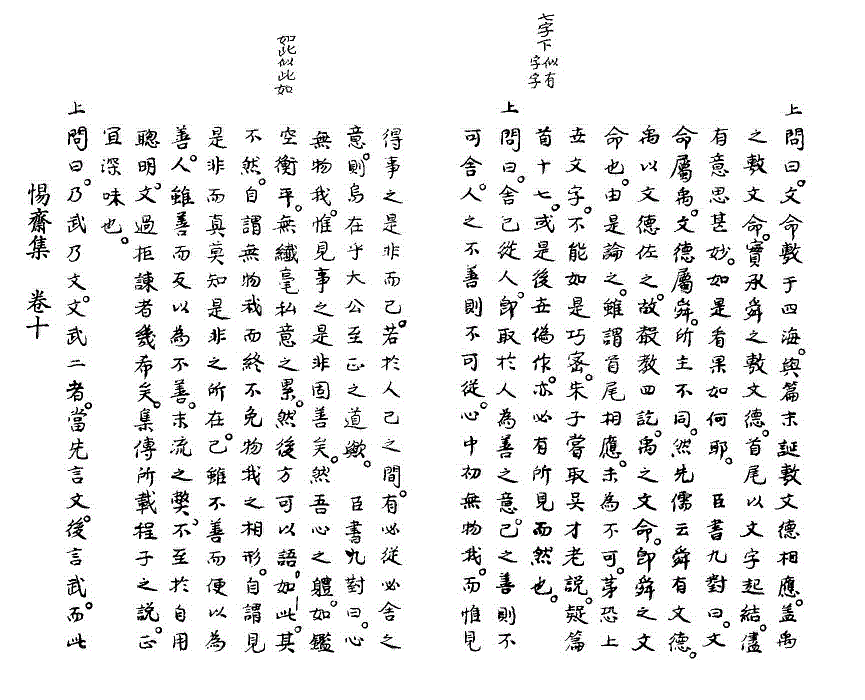 上问曰。文命敷于四海。与篇末诞敷文德相应。盖禹之敷文命。实承舜之敷文德。首尾以文字起结。尽有意思甚妙。如是看果如何耶。
上问曰。文命敷于四海。与篇末诞敷文德相应。盖禹之敷文命。实承舜之敷文德。首尾以文字起结。尽有意思甚妙。如是看果如何耶。臣书九对曰。文命属禹。文德属舜。所主不同。然先儒云舜有文德。禹以文德佐之。故声教四讫。禹之文命。即舜之文命也。由是论之。虽谓首尾相应。未为不可。第恐上世文字。不能如是巧密。朱子尝取吴才老说。疑篇首十七(七字下似有字字)。或是后世伪作。亦必有所见而然也。
上问曰。舍己从人。即取于人为善之意。己之善则不可舍。人之不善则不可从。心中初无物我。而惟见得事之是非而已。若于人己之间。有必从必舍之意。则乌在乎大公至正之道欤。
臣书九对曰。心无物我。惟见事之是非固善矣。然吾心之体。如鉴空衡平。无纤毫私意之累。然后方可以语如此(如此似此如)。其不然。自谓无物我而终不免物我之相形。自谓见是非而真莫知是非之所在。己虽不善而便以为善。人虽善而反以为不善。末流之弊。不至于自用聪明。文过拒谏者几希矣。集传所载程子之说。正宜深味也。
上问曰。乃武乃文。文武二者。当先言文。后言武。而此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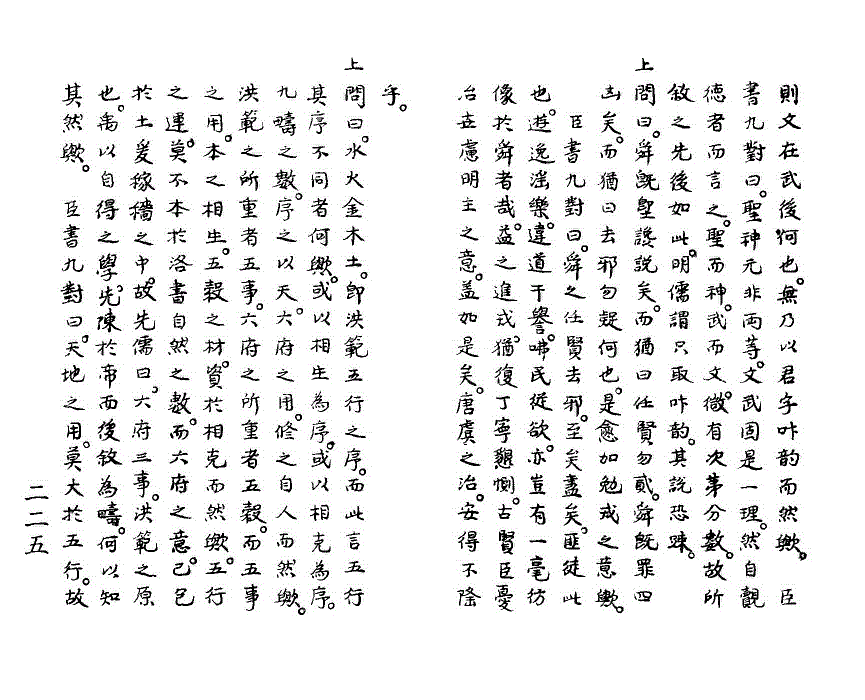 则文在武后何也。无乃以君字叶韵而然欤。
则文在武后何也。无乃以君字叶韵而然欤。臣书九对曰。圣神元非两等。文武固是一理。然自觌德者而言之。圣而神。武而文。微有次第分数。故所叙之先后如此。明儒谓只取叶韵。其说恐疏。
上问曰。舜既堲谗说矣。而犹曰任贤勿贰。舜既罪四凶矣。而犹曰去邪勿疑何也。是愈加勉戒之意欤。
臣书九对曰。舜之任贤去邪。至矣尽矣。匪徒此也。游逸淫乐。违道干誉。咈民从欲。亦岂有一毫彷像于舜者哉。益之进戒。犹复丁宁恳恻。古贤臣忧治世虑明主之意。盖如是矣。唐虞之治。安得不隆乎。
上问曰。水火金木土。即洪范五行之序。而此言五行其序不同者何欤。或以相生为序。或以相克为序。九畴之数。序之以天。六府之用。修之自人而然欤。洪范之所重者五事。六府之所重者五谷。而五事之用。本之相生。五谷之材。资于相克而然欤。五行之运。莫不本于洛书自然之数。而六府之意。已包于土爰稼穑之中。故先儒曰。六府三事。洪范之原也。禹以自得之学。先陈于帝而后叙为畴。何以知其然欤。
臣书九对曰。天地之用。莫大于五行。故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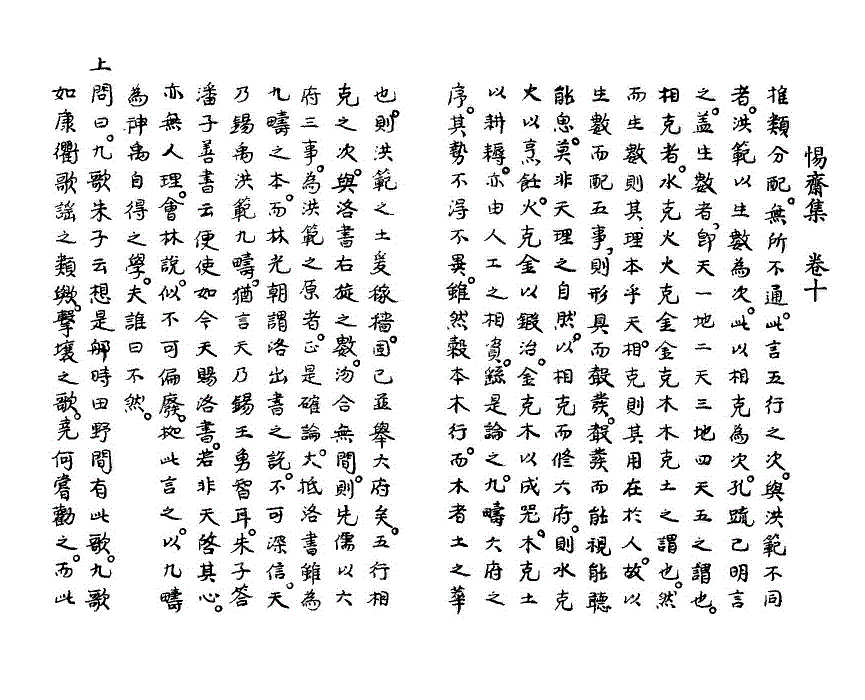 推类分配。无所不通。此言五行之次。与洪范不同者。洪范以生数为次。此以相克为次。孔疏已明言之。盖生数者。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谓也。相克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之谓也。然而生数则其理本乎天。相克则其用在于人。故以生数而配五事。则形具而声发。声发而能视能听能思。莫非天理之自然。以相克而修六府。则水克火以烹饪。火克金以锻治。金克木以成器。木克土以耕耨。亦由人工之相资。繇是论之。九畴六府之序。其势不得不异。虽然谷本木行。而木者土之华也。则洪范之土爰稼穑。固已并举六府矣。五行相克之次。与洛书右旋之数。沕合无间。则先儒以六府三事。为洪范之原者。正是确论。大抵洛书虽为九畴之本。而林光朝谓洛出书之说。不可深信。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犹言天乃锡王勇智耳。朱子答潘子善书云便使如今天赐洛书。若非天启其心。亦无人理。会林说。似不可偏废。据此言之。以九畴为神禹自得之学。夫谁曰不然。
推类分配。无所不通。此言五行之次。与洪范不同者。洪范以生数为次。此以相克为次。孔疏已明言之。盖生数者。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谓也。相克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之谓也。然而生数则其理本乎天。相克则其用在于人。故以生数而配五事。则形具而声发。声发而能视能听能思。莫非天理之自然。以相克而修六府。则水克火以烹饪。火克金以锻治。金克木以成器。木克土以耕耨。亦由人工之相资。繇是论之。九畴六府之序。其势不得不异。虽然谷本木行。而木者土之华也。则洪范之土爰稼穑。固已并举六府矣。五行相克之次。与洛书右旋之数。沕合无间。则先儒以六府三事。为洪范之原者。正是确论。大抵洛书虽为九畴之本。而林光朝谓洛出书之说。不可深信。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犹言天乃锡王勇智耳。朱子答潘子善书云便使如今天赐洛书。若非天启其心。亦无人理。会林说。似不可偏废。据此言之。以九畴为神禹自得之学。夫谁曰不然。上问曰。九歌朱子云想是那时田野间有此歌。九歌如康衢歌谣之类欤。击壤之歌。尧何尝劝之。而此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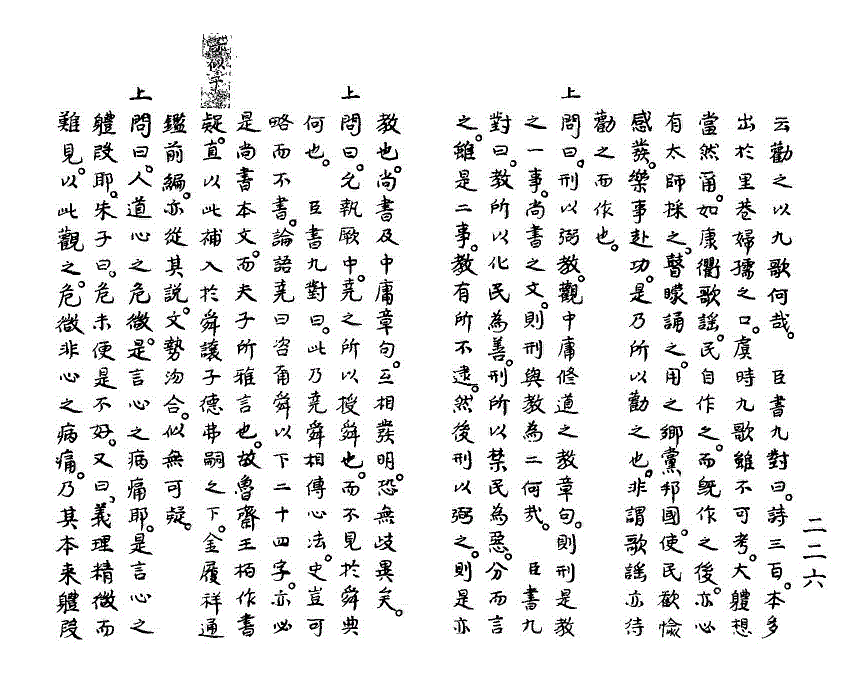 云劝之以九歌何哉。
云劝之以九歌何哉。臣书九对曰。诗三百。本多出于里巷妇孺之口。虞时九歌虽不可考。大体想当然尔。如康衢歌谣。民自作之。而既作之后。亦必有太师采之。瞽矇诵之。用之乡党邦国。使民欢愉感发。乐事赴功。是乃所以劝之也。非谓歌谣亦待劝之而作也。
上问曰。刑以弼教。观中庸修道之教章句。则刑是教之一事。尚书之文。则刑与教为二何哉。
臣书九对曰。教所以化民为善。刑所以禁民为恶。分而言之。虽是二事。教有所不逮。然后刑以弼之。则是亦教也。尚书及中庸章句。互相发明。恐无歧异矣。
上问曰。允执厥中。尧之所以授舜也。而不见于舜典何也。
臣书九对曰。此乃尧舜相传心法。史岂可略而不书。论语尧曰咨尔舜以下二十四字。亦必是尚书本文。而夫子所雅言也。故鲁斋王柏作书疑。直以此补入于舜让子(子似于)德弗嗣之下。金履祥通鉴前编。亦从其说。文势沕合。似无可疑。
上问曰。人道心之危微。是言心之病痛耶。是言心之体段耶。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又曰。义理精微而难见。以此观之。危微非心之病痛。乃其本来体段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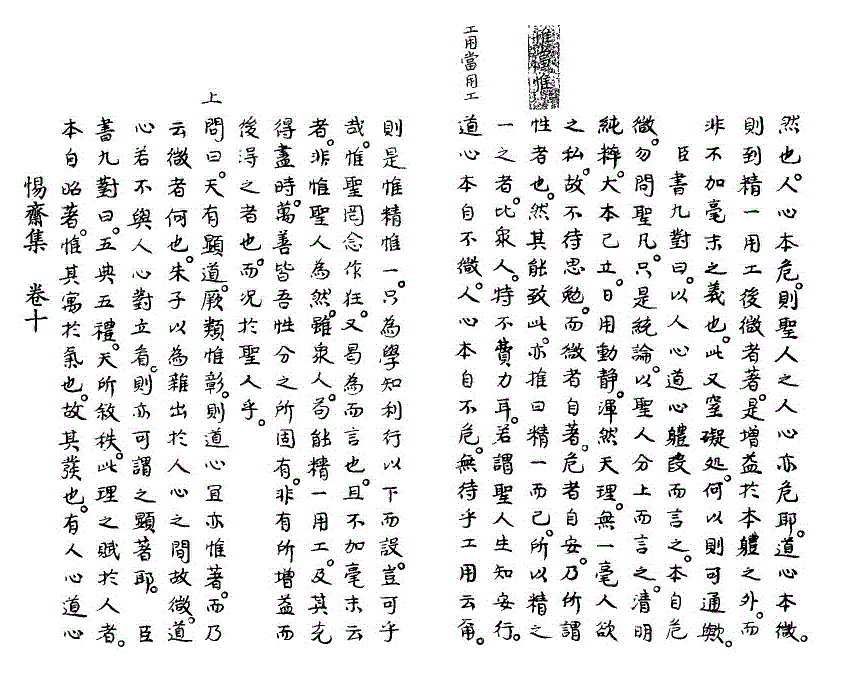 然也。人心本危。则圣人之人心亦危耶。道心本微。则到精一用工后微者著。是增益于本体之外。而非不加毫末之义也。此又窒碍处。何以则可通欤。
然也。人心本危。则圣人之人心亦危耶。道心本微。则到精一用工后微者著。是增益于本体之外。而非不加毫末之义也。此又窒碍处。何以则可通欤。臣书九对曰。以人心道心体段而言之。本自危微。勿问圣凡。只是统论。以圣人分上而言之。清明纯粹。大本已立。日用动静。浑然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故不待思勉。而微者自著。危者自安。乃所谓性者也。然其能致此。亦惟曰精一而已。所以精之一之者。比众人。特不费力耳。若谓圣人生知安行。道心本自不微。人心本自不危。无待乎用工云尔。则是惟精惟一。只为学知利行以下而设。岂可乎哉。惟圣罔念作狂。又曷为而言也。且不加毫末云者。非惟圣人为然。虽众人。苟能精一用工。及其充得尽时。万善皆吾性分之所固有。非有所增益而后得之者也。而况于圣人乎。
上问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则道心宜亦惟著。而乃云微者何也。朱子以为杂出于人心之间故微。道心若不与人心对立看。则亦可谓之显著耶。
臣书九对曰。五典五礼。天所叙秩。此理之赋于人者。本自昭著。惟其寓于气也。故其发也。有人心道心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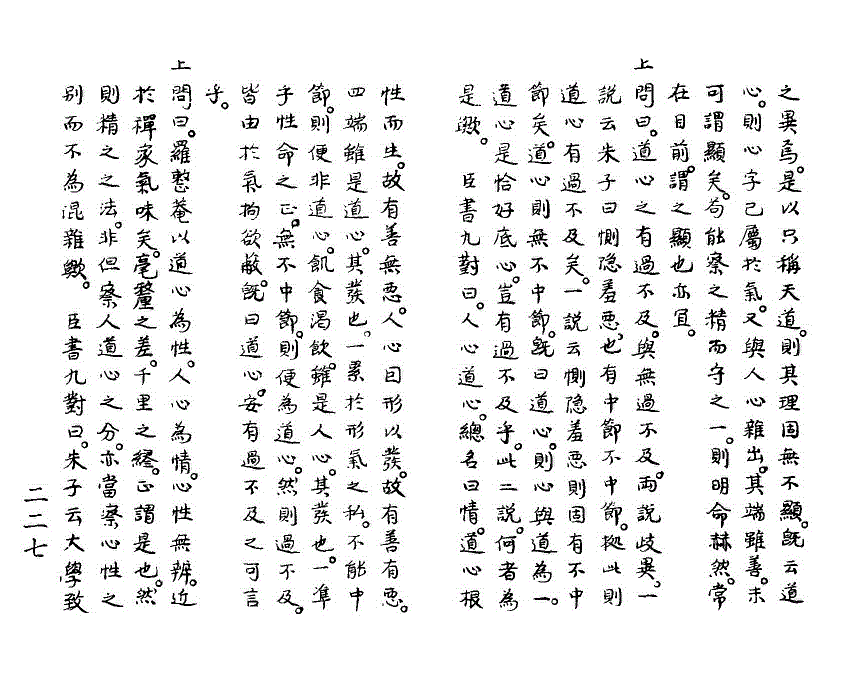 之异焉。是以只称天道。则其理固无不显。既云道心。则心字已属于气。又与人心杂出。其端虽善。未可谓显矣。苟能察之精而守之一。则明命赫然。常在目前。谓之显也亦宜。
之异焉。是以只称天道。则其理固无不显。既云道心。则心字已属于气。又与人心杂出。其端虽善。未可谓显矣。苟能察之精而守之一。则明命赫然。常在目前。谓之显也亦宜。上问曰。道心之有过不及。与无过不及。两说歧异。一说云朱子曰恻隐羞恶。也有中节不中节。据此则道心有过不及矣。一说云恻隐羞恶则固有不中节矣。道心则无不中节。既曰道心。则心与道为一。道心是恰好底心。岂有过不及乎。此二说。何者为是欤。
臣书九对曰。人心道心。总名曰情。道心根性而生。故有善无恶。人心因形以发。故有善有恶。四端虽是道心。其发也。一累于形气之私。不能中节。则便非道心。饥食渴饮。虽是人心。其发也。一准乎性命之正。无不中节。则便为道心。然则过不及。皆由于气拘欲蔽。既曰道心。安有过不及之可言乎。
上问曰。罗整庵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心性无辨。近于禅家气味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缪。正谓是也。然则精之之法。非但察人道心之分。亦当察心性之别而不为混杂欤。
臣书九对曰。朱子云大学致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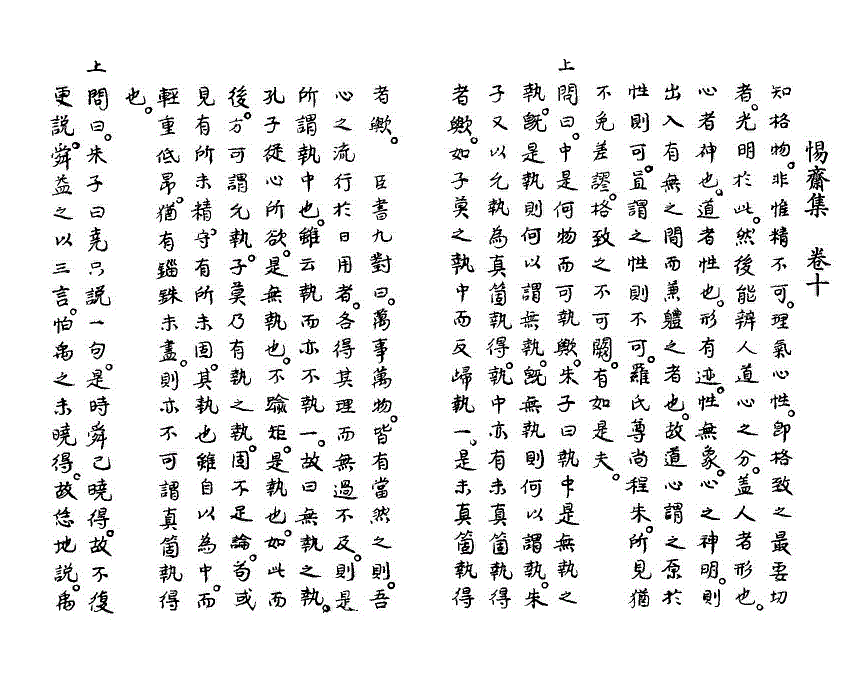 知格物。非惟精不可。理气心性。即格致之最要切者。光明于此。然后能辨人道心之分。盖人者形也。心者神也。道者性也。形有迹。性无象。心之神明。则出入有无之间而兼体之者也。故道心谓之原于性则可。直谓之性则不可。罗氏尊尚程朱。所见犹不免差谬。格致之不可阙。有如是夫。
知格物。非惟精不可。理气心性。即格致之最要切者。光明于此。然后能辨人道心之分。盖人者形也。心者神也。道者性也。形有迹。性无象。心之神明。则出入有无之间而兼体之者也。故道心谓之原于性则可。直谓之性则不可。罗氏尊尚程朱。所见犹不免差谬。格致之不可阙。有如是夫。上问曰。中是何物而可执欤。朱子曰执中是无执之执。既是执则何以谓无执。既无执则何以谓执。朱子又以允执为真个执得。执中亦有未真个执得者欤。如子莫之执中而反归执一。是未真个执得者欤。
臣书九对曰。万事万物。皆有当然之则。吾心之流行于日用者。各得其理而无过不及。则是所谓执中也。虽云执而亦不执一。故曰无执之执。孔子从心所欲。是无执也。不踰矩。是执也。如此而后。方可谓允执。子莫乃有执之执。固不足论。苟或见有所未精。守有所未固。其执也虽自以为中。而轻重低昂。犹有锱铢未尽。则亦不可谓真个执得也。
上问曰。朱子曰尧只说一句。是时舜已晓得。故不复更说。舜益之以三言。怕禹之未晓得。故恁地说。禹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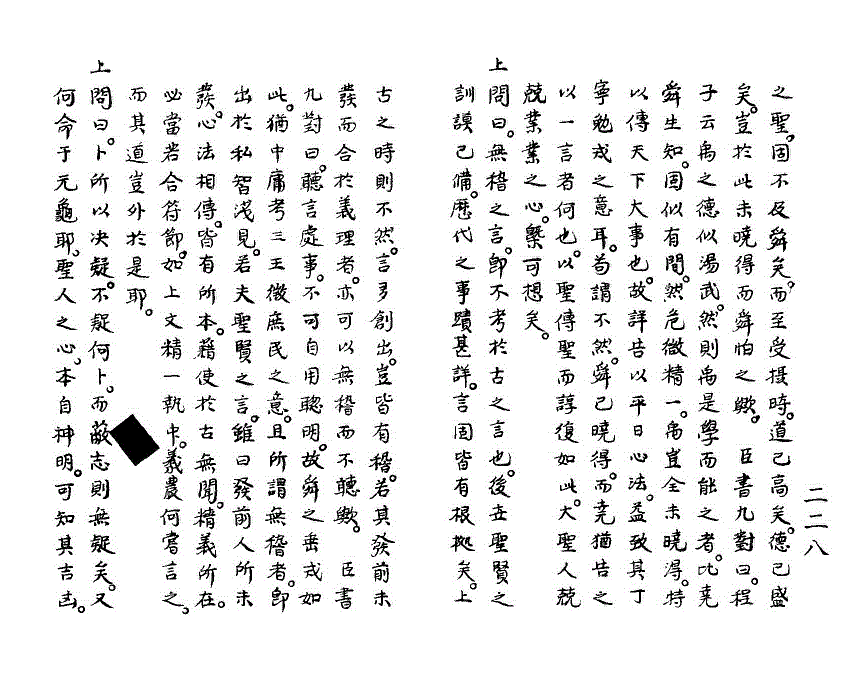 之圣。固不及舜矣。而至受摄时。道已高矣。德已盛矣。岂于此未晓得而舜怕之欤。
之圣。固不及舜矣。而至受摄时。道已高矣。德已盛矣。岂于此未晓得而舜怕之欤。臣书九对曰。程子云禹之德似汤武。然则禹是学而能之者。比尧舜生知。固似有间。然危微精一。禹岂全未晓得。特以传天下大事也。故详告以平日心法。益致其丁宁勉戒之意耳。苟谓不然。舜已晓得。而尧犹告之以一言者何也。以圣传圣而谆复如此。大圣人兢兢业业之心。槩可想矣。
上问曰。无稽之言。即不考于古之言也。后世圣贤之训谟已备。历代之事迹甚详。言固皆有根据矣。上古之时则不然。言多创出。岂皆有稽。若其发前未发而合于义理者。亦可以无稽而不听欤。
臣书九对曰。听言处事。不可自用聪明。故舜之垂戒如此。犹中庸考三王徵庶民之意。且所谓无稽者。即出于私智浅见。若夫圣贤之言。虽曰发前人所未发。心法相传。皆有所本。藉使于古无闻。精义所在。必当若合符节。如上文精一执中。羲农何尝言之。而其道岂外于是耶。
上问曰。卜所以决疑。不疑何卜。而蔽志则无疑矣。又何命于元龟耶。圣人之心。本自神明。可知其吉凶。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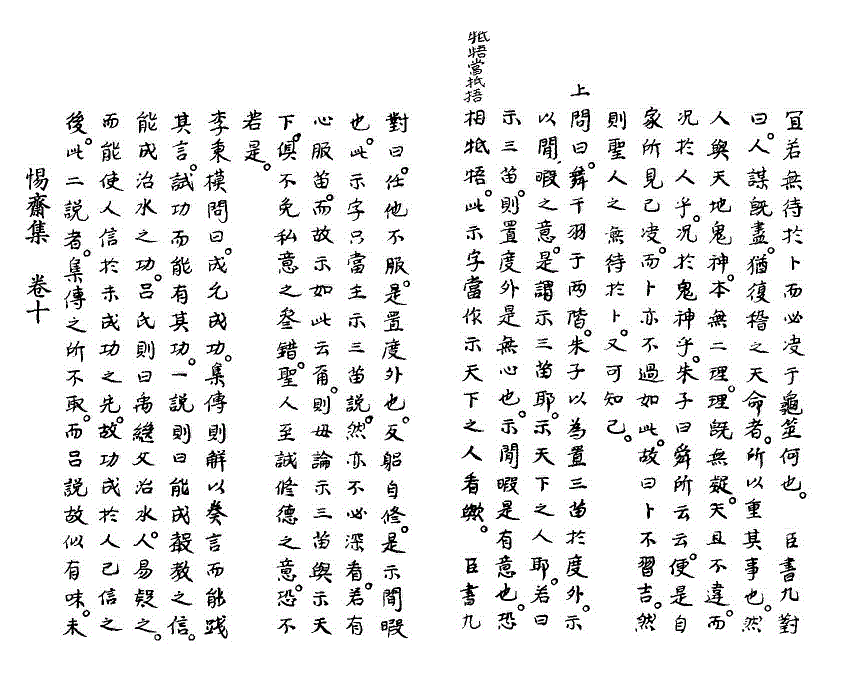 宜若无待于卜而必决于龟筮何也。
宜若无待于卜而必决于龟筮何也。臣书九对曰。人谋既尽。犹复稽之天命者。所以重其事也。然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理既无疑。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朱子曰舜所云云。便是自家所见已决。而卜亦不过如此。故曰卜不习吉。然则圣人之无待于卜。又可知已。
上问曰。舞干羽于两阶。朱子以为置三苗于度外。示以閒暇之意。是谓示三苗耶。示天下之人耶。若曰示三苗。则置度外是无心也。示閒暇是有意也。恐相抵捂。此示字当作示天下之人看欤。
臣书九对曰。任他不服。是置度外也。反躬自修。是示间暇也。此示字只当主示三苗说。然亦不必深看。若有心服苗。而故示如此云尔。则毋论示三苗与示天下。俱不免私意之参错。圣人至诚修德之意。恐不若是。
李秉模问曰。成允成功。集传则解以奏言而能践其言。试功而能有其功。一说则曰能成声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吕氏则曰禹继父治水。人易疑之。而能使人信于未成功之先。故功成于人已信之后。此二说者。集传之所不取。而吕说故似有味。未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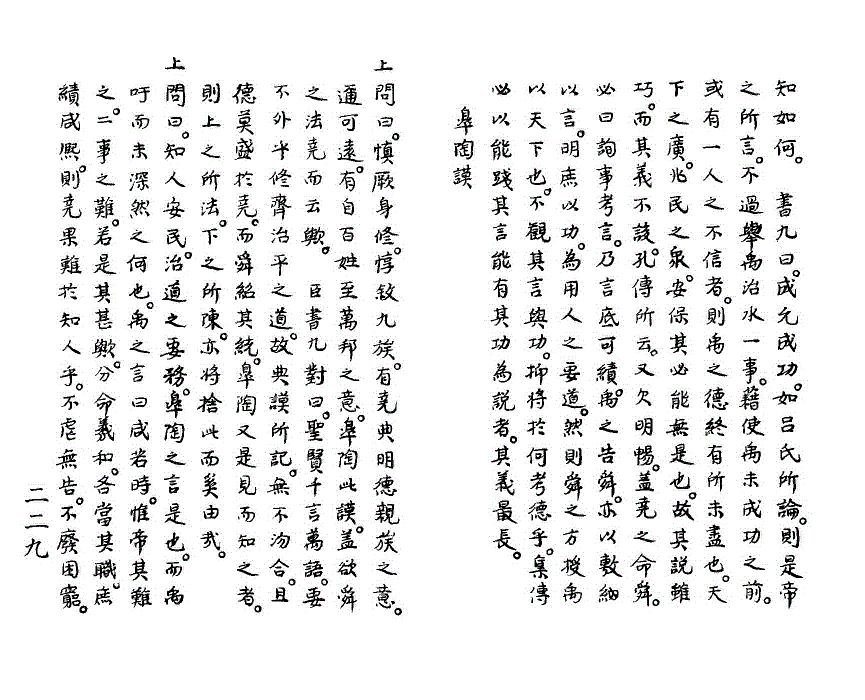 知如何。
知如何。书九曰。成允成功。如吕氏所论。则是帝之所言。不过举禹治水一事。藉使禹未成功之前。或有一人之不信者。则禹之德终有所未尽也。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安保其必能无是也。故其说虽巧。而其义不该。孔传所云。又欠明畅。盖尧之命舜。必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禹之告舜。亦以敷纳以言。明庶以功。为用人之要道。然则舜之方授禹以天下也。不观其言与功。抑将于何考德乎。集传必以能践其言能有其功为说者。其义最长。
皋陶谟
上问曰。慎厥身修。惇叙九族。有尧典明德亲族之意。迩可远。有自百姓至万邦之意。皋陶此谟。盖欲舜之法尧而云欤。
臣书九对曰。圣贤千言万语。要不外乎修齐治平之道。故典谟所记。无不沕合。且德莫盛于尧。而舜绍其统。皋陶又是见而知之者。则上之所法。下之所陈。亦将舍此而奚由哉。
上问曰。知人安民。治道之要务。皋陶之言是也。而禹吁而未深然之何也。禹之言曰咸若时。惟帝其难之。二事之难。若是其甚欤。分命羲和。各当其职。庶绩咸熙。则尧果难于知人乎。不虐无告。不废困穷。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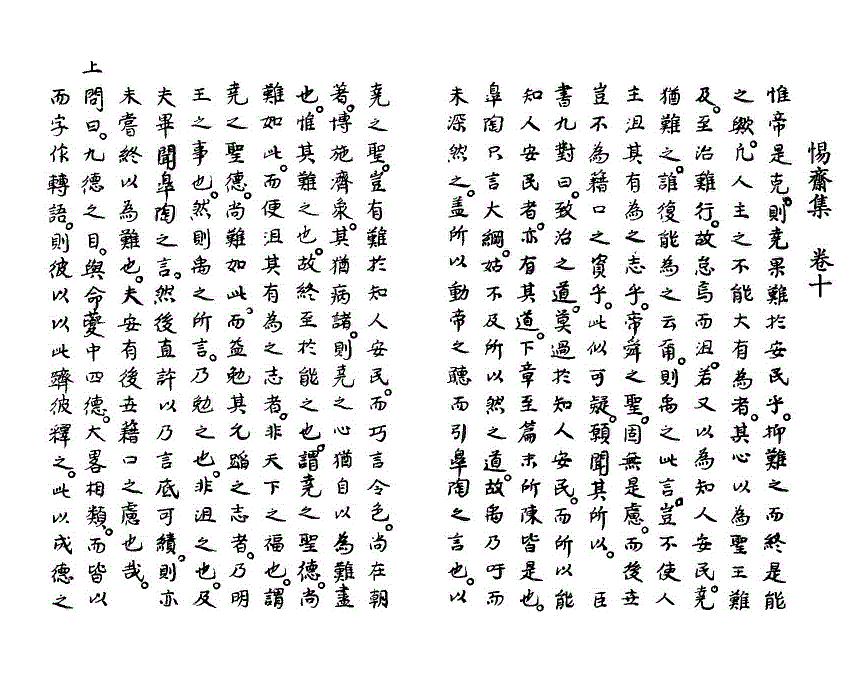 惟帝是克。则尧果难于安民乎。抑难之而终是能之欤。凡人主之不能大有为者。其心以为圣王难及。至治难行。故怠焉而沮。若又以为知人安民。尧犹难之。谁复能为之云尔。则禹之此言。岂不使人主沮其有为之志乎。帝舜之圣。固无是虑。而后世岂不为藉口之资乎。此似可疑。愿闻其所以。
惟帝是克。则尧果难于安民乎。抑难之而终是能之欤。凡人主之不能大有为者。其心以为圣王难及。至治难行。故怠焉而沮。若又以为知人安民。尧犹难之。谁复能为之云尔。则禹之此言。岂不使人主沮其有为之志乎。帝舜之圣。固无是虑。而后世岂不为藉口之资乎。此似可疑。愿闻其所以。臣书九对曰。致治之道。莫过于知人安民。而所以能知人安民者。亦有其道。下章至篇末所陈皆是也。皋陶只言大纲。姑不及所以然之道。故禹乃吁而未深然之。盖所以动帝之听而引皋陶之言也。以尧之圣。岂有难于知人安民。而巧言令色。尚在朝著。博施济众。其犹病诸。则尧之心犹自以为难尽也。惟其难之也。故终至于能之也。谓尧之圣德。尚难如此。而便沮其有为之志者。非天下之福也。谓尧之圣德。尚难如此。而益勉其允蹈之志者。乃明王之事也。然则禹之所言。乃勉之也。非沮之也。及夫毕闻皋陶之言。然后直许以乃言底可绩。则亦未尝终以为难也。夫安有后世藉口之虑也哉。
上问曰。九德之目。与命夔中四德。大略相类。而皆以而字作转语。则彼以以此跻彼释之。此以成德之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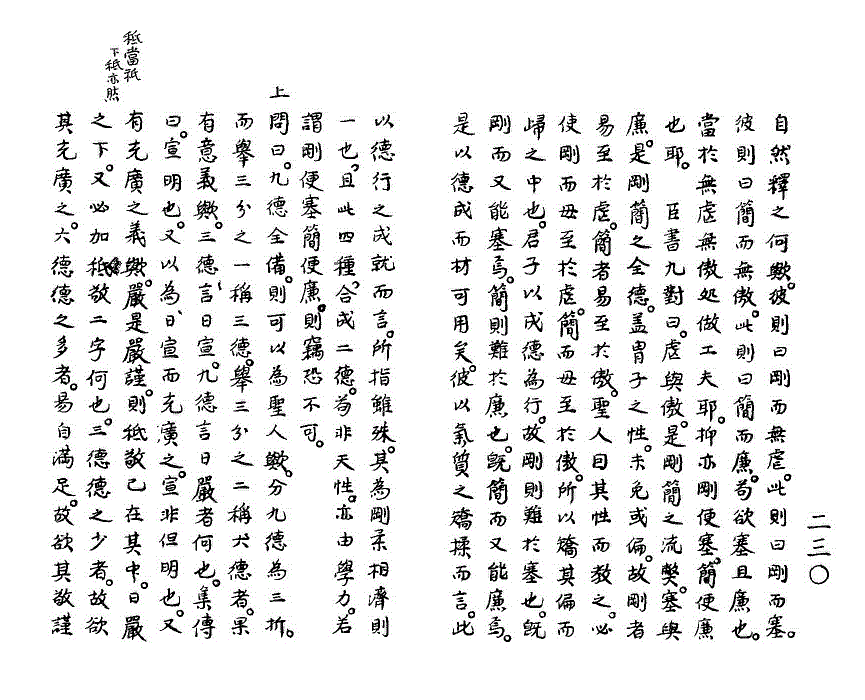 自然释之何欤。彼则曰刚而无虐。此则曰刚而塞。彼则曰简而无傲。此则曰简而廉。苟欲塞且廉也。当于无虐无傲处做工夫耶。抑亦刚便塞。简便廉也耶。
自然释之何欤。彼则曰刚而无虐。此则曰刚而塞。彼则曰简而无傲。此则曰简而廉。苟欲塞且廉也。当于无虐无傲处做工夫耶。抑亦刚便塞。简便廉也耶。臣书九对曰。虐与傲。是刚简之流弊。塞与廉。是刚简之全德。盖胄子之性。未免或偏。故刚者易至于虐。简者易至于傲。圣人因其性而教之。必使刚而毋至于虐。简而毋至于傲。所以矫其偏而归之中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故刚则难于塞也。既刚而又能塞焉。简则难于廉也。既简而又能廉焉。是以德成而材可用矣。彼以气质之矫揉而言。此以德行之成就而言。所指虽殊。其为刚柔相济则一也。且此四种。合成二德。苟非天性。亦由学力。若谓刚便塞简便廉。则窃恐不可。
上问曰。九德全备。则可以为圣人欤。分九德为三折。而举三分之一称三德。举三分之二称六德者。果有意义欤。三德言日宣。九德言日严者何也。集传曰。宣明也。又以为日宣而充广之。宣非但明也。又有充广之义欤。严是严谨。则祗敬已在其中。日严之下。又必加祗敬二字何也。三德德之少者。故欲其充广之。六德德之多者。易自满足。故欲其敬谨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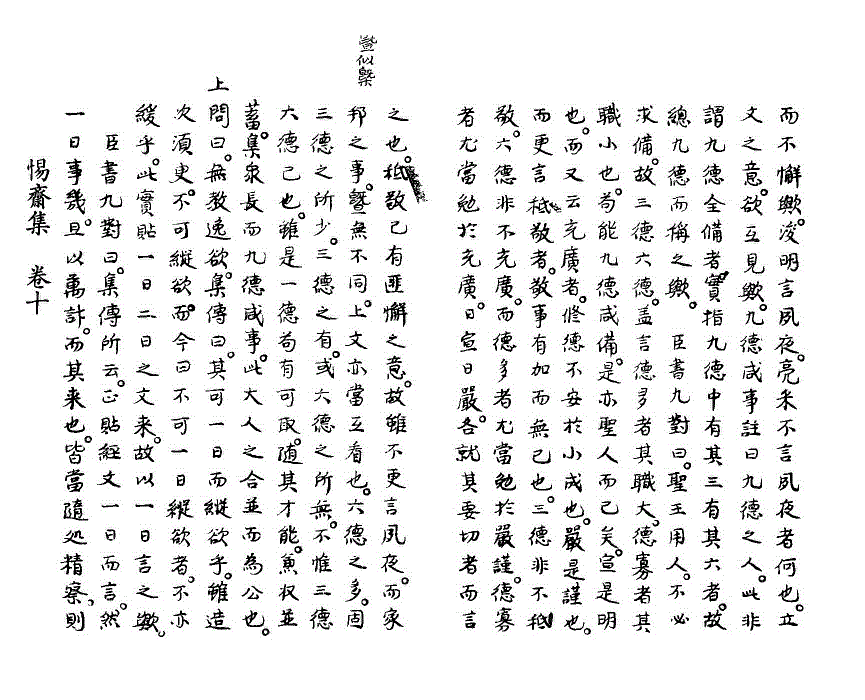 而不懈欤。浚明言夙夜。亮采不言夙夜者何也。立文之意。欲互见欤。九德咸事注曰九德之人。此非谓九德全备者。实指九德中有其三有其六者。故总九德而称之欤。
而不懈欤。浚明言夙夜。亮采不言夙夜者何也。立文之意。欲互见欤。九德咸事注曰九德之人。此非谓九德全备者。实指九德中有其三有其六者。故总九德而称之欤。臣书九对曰。圣王用人。不必求备。故三德六德。盖言德多者其职大。德寡者其职小也。苟能九德咸备。是亦圣人而已矣。宣是明也。而又云充广者。修德不安于小成也。严是谨也。而更言祗敬者。敬事有加而无已也。三德非不祗敬。六德非不充广。而德多者尤当勉于严谨。德寡者尤当勉于充广。日宣日严。各就其要切者而言之也。祗敬已有匪懈之意。故虽不更言夙夜。而家邦之事。暨(暨似槩)无不同。上文亦当互看也。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无。不惟三德六德已也。虽是一德苟有可取。随其才能。兼收并蓄。集众长而九德咸事。此大人之合并而为公也。
上问曰。无教逸欲。集传曰。其可一日而纵欲乎。虽造次须臾。不可纵欲。而今曰不可一日纵欲者。不亦缓乎。此实贴一日二日之文来。故以一日言之欤。
臣书九对曰。集传所云。正贴经文一日而言。然一日事几。且以万计。而其来也。皆当随处精察。则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1L 页
 兢业之心。不敢少懈者。已包于其中。语虽似缓。意则自密。
兢业之心。不敢少懈者。已包于其中。语虽似缓。意则自密。上问曰。天工人代。此天字屡见于书中矣。天有以理言之天。有以形体言之天。此天字当以何看耶。
臣书九对曰。天字固当以苍苍者言。然苍苍之天。即是以理言之。天以其主宰而谓之帝。以其性情而谓之乾。其宲一也。叙秩命讨。皆是天理。但苍苍者不能自为。不得不付之人而治之。故曰天工人其代之。
上问曰。天叙以下。言圣人奉天之事。礼乐刑政四者。乐亦出于天。而此不言乐何也。
臣书九对曰。典礼刑赏。本于天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乐之理亦出于天。典礼刑赏。各得其正。天理无所乖沴。人心无不悦豫。是所谓和衷也。和者乐之本。皋陶虽不言乐。其理则固已包括无馀矣。
上问曰。天高听卑。日监在玆。则天之聪明大矣。何必曰自我民聪明。雨露以生之。雪霜以杀之。天之明畏著矣。又何必曰自我民明畏。宋臣张九成之言曰。勿以苍苍者为天。而求诸视听言动之间。人之视听言动。皆是天也。天人一理。物我同得。则民与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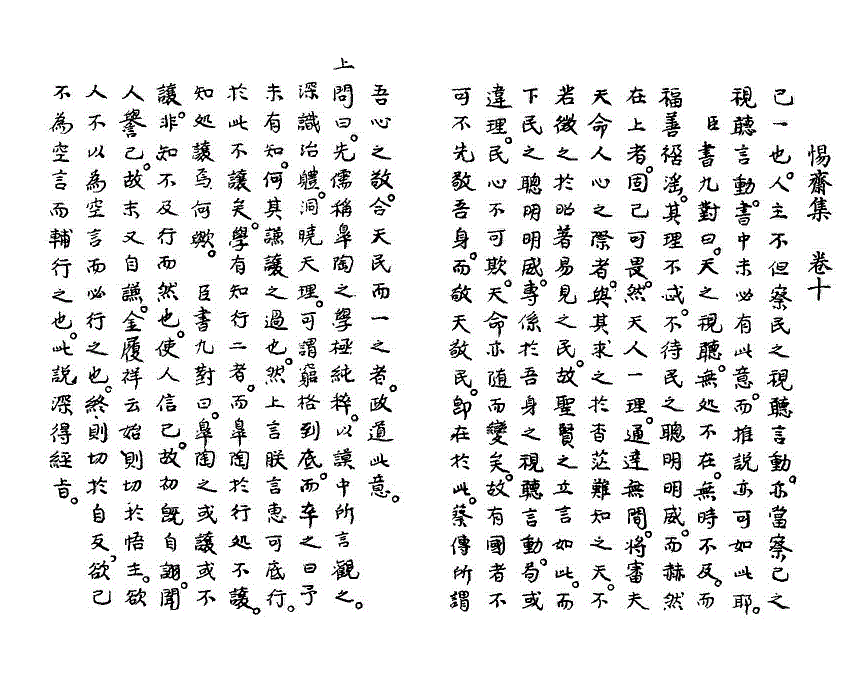 己一也。人主不但察民之视听言动。亦当察己之视听言动。书中未必有此意。而推说亦可如此耶。
己一也。人主不但察民之视听言动。亦当察己之视听言动。书中未必有此意。而推说亦可如此耶。臣书九对曰。天之视听。无处不在。无时不及。而福善𥙯淫。其理不忒。不待民之聪明明威。而赫然在上者。固已可畏。然天人一理。通达无间。将审夫天命人心之际者。与其求之于杳茫难知之天。不若徵之于昭著易见之民。故圣贤之立言如此。而下民之聪明明威。专系于吾身之视听言动。苟或违理。民心不可欺。天命亦随而变矣。故有国者不可不先敬吾身。而敬天敬民。即在于此。蔡传所谓吾心之敬。合天民而一之者。政道此意。
上问曰。先儒称皋陶之学极纯粹。以谟中所言观之。深识治体。洞晓天理。可谓穷格到底。而卒之曰予未有知。何其谦让之过也。然上言朕言惠可底行。于此不让矣。学有知行二者。而皋陶于行处不让。知处让焉何欤。
臣书九对曰。皋陶之或让或不让。非知不及行而然也。使人信己。故初既自诩。闻人誉己。故末又自谦。金履祥云始则切于悟主。欲人不以为空言而必行之也。终则切于自反。欲己不为空言而辅行之也。此说深得经旨。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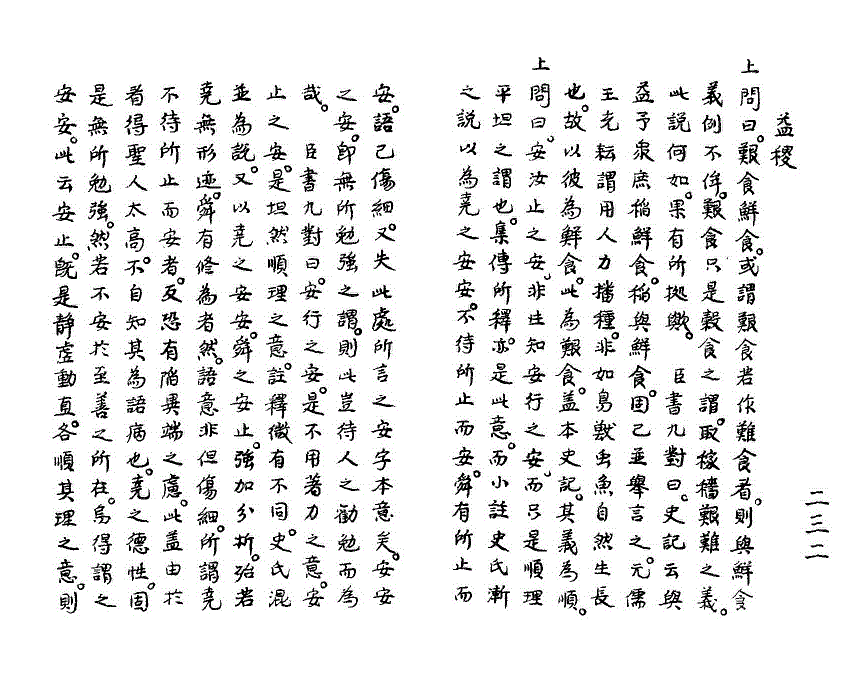 益稷
益稷上问曰。艰食鲜食。或谓艰食若作难食看。则与鲜食义例不侔。艰食只是谷食之谓。取稼穑艰难之义。此说何如。果有所据欤。
臣书九对曰。史记云与益予众庶稻鲜食。稻与鲜食。固已并举言之。元儒王充耘谓用人力播种。非如鸟兽虫鱼自然生长也。故以彼为鲜食。此为艰食。盖本史记。其义为顺。
上问曰。安汝止之安。非生知安行之安。而只是顺理平坦之谓也。集传所释。亦是此意。而小注史氏渐之说以为尧之安安。不待所止而安。舜有所止而安。语已伤细。又失此处所言之安字本意矣。安安之安。即无所勉强之谓。则此岂待人之劝勉而为哉。
臣书九对曰。安行之安。是不用著力之意。安止之安。是坦然顺理之意。注释微有不同。史氏混并为说。又以尧之安安。舜之安止。强加分析。殆若尧无形迹。舜有修为者然。语意非但伤细。所谓尧不待所止而安者。反恐有陷异端之虑。此盖由于看得圣人太高。不自知其为语病也。尧之德性。固是无所勉强。然若不安于至善之所在。乌得谓之安安。此云安止。既是静虚动直。各顺其理之意。则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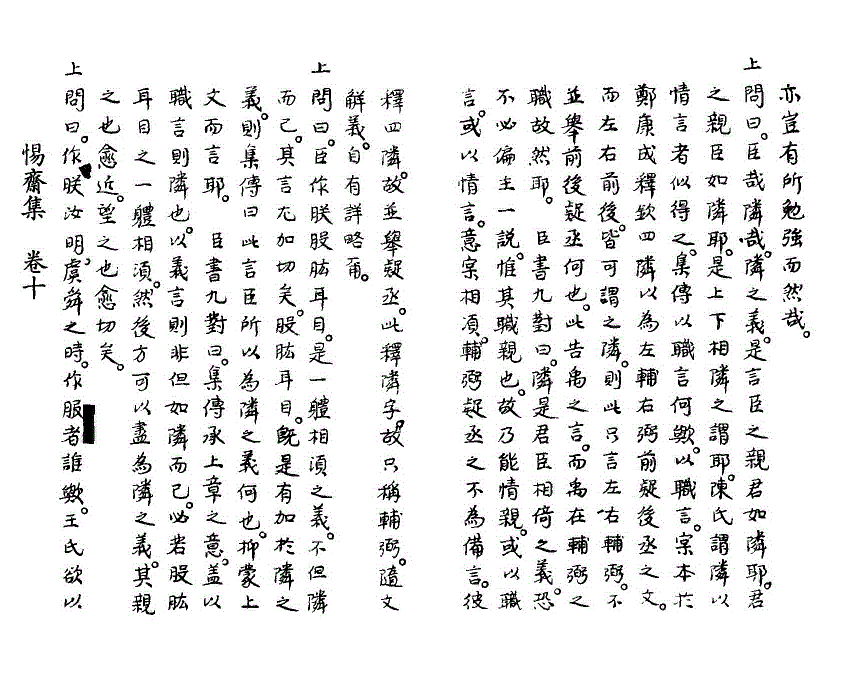 亦岂有所勉强而然哉。
亦岂有所勉强而然哉。上问曰。臣哉邻哉。邻之义。是言臣之亲君如邻耶。君之亲臣如邻耶。是上下相邻之谓耶。陈氏谓邻以情言者似得之。集传以职言何欤。以职言。宲本于郑康成释钦四邻以为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之文。而左右前后。皆可谓之邻。则此只言左右辅弼。不并举前后疑丞何也。此告禹之言。而禹在辅弼之职故然耶。
臣书九对曰。邻是君臣相倚之义。恐不必偏主一说。惟其职亲也。故乃能情亲。或以职言。或以情言。意宲相须。辅弼疑丞之不为备言。彼释四邻。故并举疑丞。此释邻字。故只称辅弼。随文解义。自有详略尔。
上问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一体相须之义。不但邻而已。其言尤加切矣。股肱耳目。既是有加于邻之义。则集传曰此言臣所以为邻之义何也。抑蒙上文而言耶。
臣书九对曰。集传承上章之意。盖以职言则邻也。以义言则非但如邻而已。必若股肱耳目之一体相须。然后方可以尽为邻之义。其亲之也愈近。望之也愈切矣。
上问曰。作朕汝明。虞舜之时。作服者谁欤。王氏欲以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3L 页
 作服归之伯夷。果有所考欤。祭重盛服。且有品节。如周礼所谓祀上帝大裘。享先王衮冕。祀山川毳冕之类是已。则伯夷典祭礼之官。故意其制祭服而然欤。唐虞之时。不别立司服之官。而使典礼者兼掌衣服欤。
作服归之伯夷。果有所考欤。祭重盛服。且有品节。如周礼所谓祀上帝大裘。享先王衮冕。祀山川毳冕之类是已。则伯夷典祭礼之官。故意其制祭服而然欤。唐虞之时。不别立司服之官。而使典礼者兼掌衣服欤。臣书九对曰。尧典秩宗。即周官宗伯。舜时官制。虽不可详。司服既是宗伯之属。郑玄周礼注。引国语云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宜者为之宗。王安石谓秩宗作服。盖亦有据。
上问曰。大抵十二章之制。天子之服也。先儒以上六为上衣。下六为下裳。而诸侯八章,卿六章,大夫四章。此虞制也。周制日月星辰画于旂。冕服九章而已。公亦九章而已。自侯伯杀之。然则天子与卿。固无别于黼章之数乎。周制之不用上六下六之数者。抑何义也。
臣书九对曰。虞制天子之服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卿加黼黻为六章。注疏之说盖如此。郑玄谓周制冕服九章。一龙二山三华虫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而衣五章画以为缋。裳四章饰以为绣。惟日月星辰画于旌旗。与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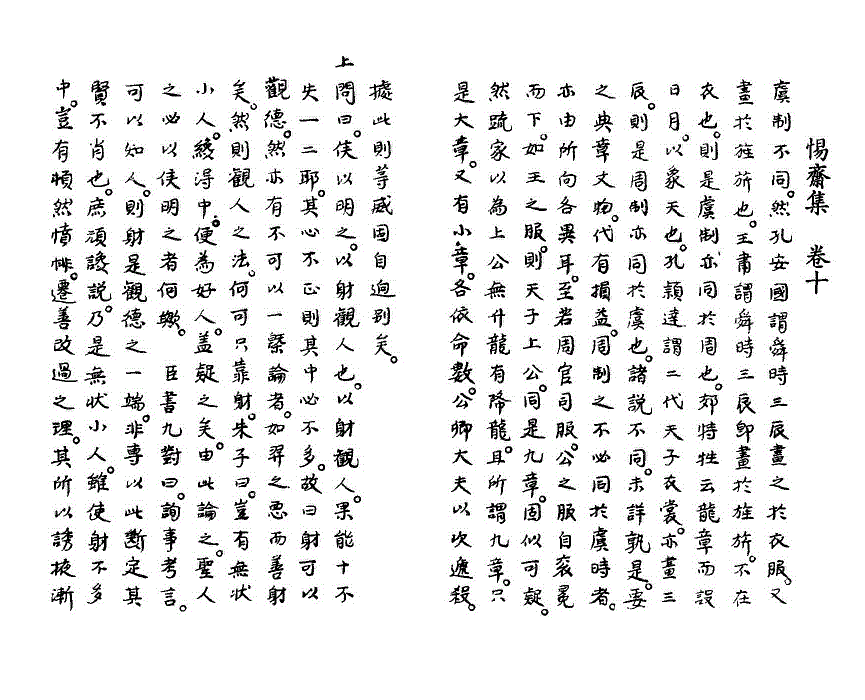 虞制不同。然孔安国谓舜时三辰画之于衣服。又画于旌旂也。王肃谓舜时三辰即画于旌旂。不在衣也。则是虞制亦同于周也。郊特牲云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孔颖达谓二代天子衣裳。亦画三辰。则是周制亦同于虞也。诸说不同。未详孰是。要之典章文物。代有损益。周制之不必同于虞时者。亦由所向各异耳。至若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则天子上公。同是九章。固似可疑。然疏家以为上公无升龙有降龙。且所谓九章。只是大章。又有小章。各依命数。公卿大夫以次递杀。据此则等威固自迥别矣。
虞制不同。然孔安国谓舜时三辰画之于衣服。又画于旌旂也。王肃谓舜时三辰即画于旌旂。不在衣也。则是虞制亦同于周也。郊特牲云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孔颖达谓二代天子衣裳。亦画三辰。则是周制亦同于虞也。诸说不同。未详孰是。要之典章文物。代有损益。周制之不必同于虞时者。亦由所向各异耳。至若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则天子上公。同是九章。固似可疑。然疏家以为上公无升龙有降龙。且所谓九章。只是大章。又有小章。各依命数。公卿大夫以次递杀。据此则等威固自迥别矣。上问曰。侯以明之。以射观人也。以射观人。果能十不失一二耶。其心不正则其中必不多。故曰射可以观德。然亦有不可以一槩论者。如羿之恶而善射矣。然则观人之法。何可只靠射。朱子曰。岂有无状小人。才得中。便为好人。盖疑之矣。由此论之。圣人之必以侯明之者何欤。
臣书九对曰。询事考言。可以知人。则射是观德之一端。非专以此断定其贤不肖也。庶顽谗说。乃是无状小人。虽使射不多中。岂有顿然愤悱。迁善改过之理。其所以诱掖渐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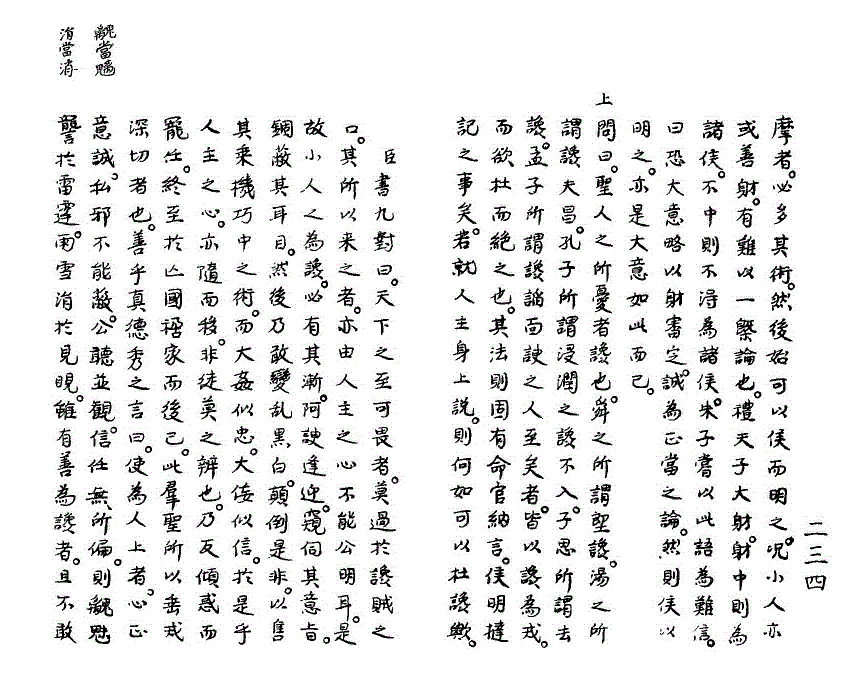 摩者。必多其术。然后始可以侯而明之。况小人亦或善射。有难以一槩论也。礼天子大射。射中则为诸侯。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朱子尝以此语为难信。曰恐大意略以射审定。诚为正当之论。然则侯以明之。亦是大意如此而已。
摩者。必多其术。然后始可以侯而明之。况小人亦或善射。有难以一槩论也。礼天子大射。射中则为诸侯。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朱子尝以此语为难信。曰恐大意略以射审定。诚为正当之论。然则侯以明之。亦是大意如此而已。上问曰。圣人之所忧者谗也。舜之所谓堲谗。汤之所谓谗夫昌。孔子所谓浸润之谗不入。子思所谓去谗。孟子所谓谗谄面谀之人至矣者。皆以谗为戒。而欲杜而绝之也。其法则固有命官纳言。侯明挞记之事矣。若就人主身上说。则何如可以杜谗欤。
臣书九对曰。天下之至可畏者。莫过于谗贼之口。其所以来之者。亦由人主之心不能公明耳。是故小人之为谗。必有其渐。阿谀逢迎。窥伺其意旨。锢蔽其耳目。然后乃敢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以售其乘机巧中之术。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于是乎人主之心。亦随而移。非徒莫之辨也。乃反倾惑而宠任。终至于亡国𥙯家而后已。此群圣所以垂戒深切者也。善乎真德秀之言曰。使为人上者。心正意诚。私邪不能蔽。公听并观。信任无所偏。则魑魅詟于雷霆。雨雪消于见睍。虽有善为谗者。且不敢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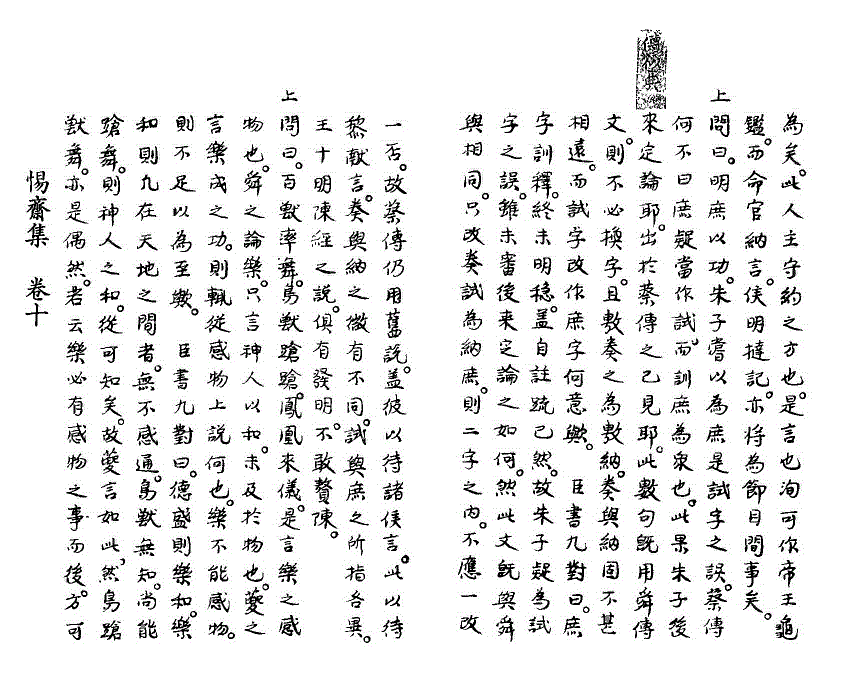 为矣。此人主守约之方也。是言也洵可作帝王龟鉴。而命官纳言。侯明挞记。亦将为节目间事矣。
为矣。此人主守约之方也。是言也洵可作帝王龟鉴。而命官纳言。侯明挞记。亦将为节目间事矣。上问曰。明庶以功。朱子尝以为庶是试字之误。蔡传何不曰庶疑当作试。而训庶为众也。此果朱子后来定论耶。出于蔡传之己见耶。此数句既用舜传(传似典)文。则不必换字。且敷奏之为敷纳。奏与纳固不甚相远。而试字改作庶字何意欤。
臣书九对曰。庶字训释。终未明稳。盖自注疏已然。故朱子疑为试字之误。虽未审后来定论之如何。然此文既与舜与相同。只改奏试为纳庶。则二字之内。不应一改一否。故蔡传仍用旧说。盖彼以待诸侯言。此以待黎献言。奏与纳之微有不同。试与庶之所指各异。王十明陈经之说。俱有发明。不敢赘陈。
上问曰。百兽率舞。鸟兽跄跄。凤凰来仪。是言乐之感物也。舜之论乐。只言神人以和。未及于物也。夔之言乐成之功。则辄从感物上说何也。乐不能感物。则不足以为至欤。
臣书九对曰。德盛则乐和。乐和则凡在天地之间者。无不感通。鸟兽无知。尚能跄舞。则神人之和。从可知矣。故夔言如此。然鸟跄兽舞。亦是偶然。若云乐必有感物之事而后。方可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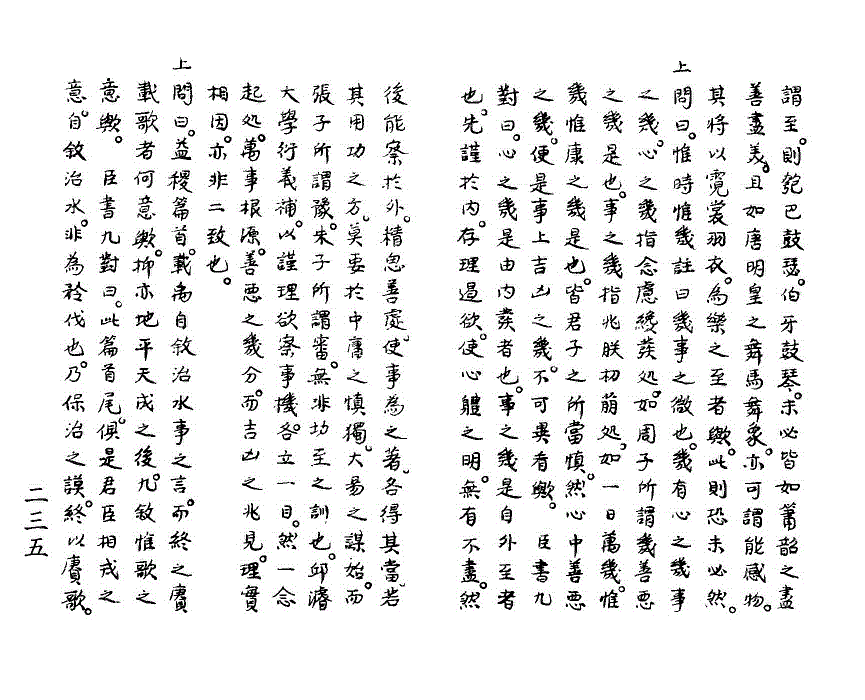 谓至。则匏巴鼓瑟。伯牙鼓琴。未必皆如箫韶之尽善尽美。且如唐明皇之舞马舞象。亦可谓能感物。其将以霓裳羽衣。为乐之至者欤。此则恐未必然。
谓至。则匏巴鼓瑟。伯牙鼓琴。未必皆如箫韶之尽善尽美。且如唐明皇之舞马舞象。亦可谓能感物。其将以霓裳羽衣。为乐之至者欤。此则恐未必然。上问曰。惟时惟几注曰几事之微也。几有心之几事之几。心之几指念虑才发处。如周子所谓几善恶之几是也。事之几指兆朕初萌处。如一日万几。惟几惟康之几是也。皆君子之所当慎。然心中善恶之几。便是事上吉凶之几。不可异看欤。
臣书九对曰。心之几是由内发者也。事之几是自外至者也。先谨于内。存理遏欲。使心体之明。无有不尽。然后能察于外。精思善处。使事为之著。各得其当。若其用功之方。莫要于中庸之慎独。大易之谋始。而张子所谓豫。朱子所谓审。无非切至之训也。邱浚大学衍义补。以谨理欲察事机。各立一目。然一念起处。万事根源。善恶之几分。而吉凶之兆见。理实相因。亦非二致也。
上问曰。益稷篇首。载禹自叙治水事之言。而终之赓载歌者何意欤。抑亦地平天成之后。九叙惟歌之意欤。
臣书九对曰。此篇首尾。俱是君臣相戒之意。自叙治水。非为矜伐也。乃保治之谟。终以赓歌。
惕斋集卷之十 第 2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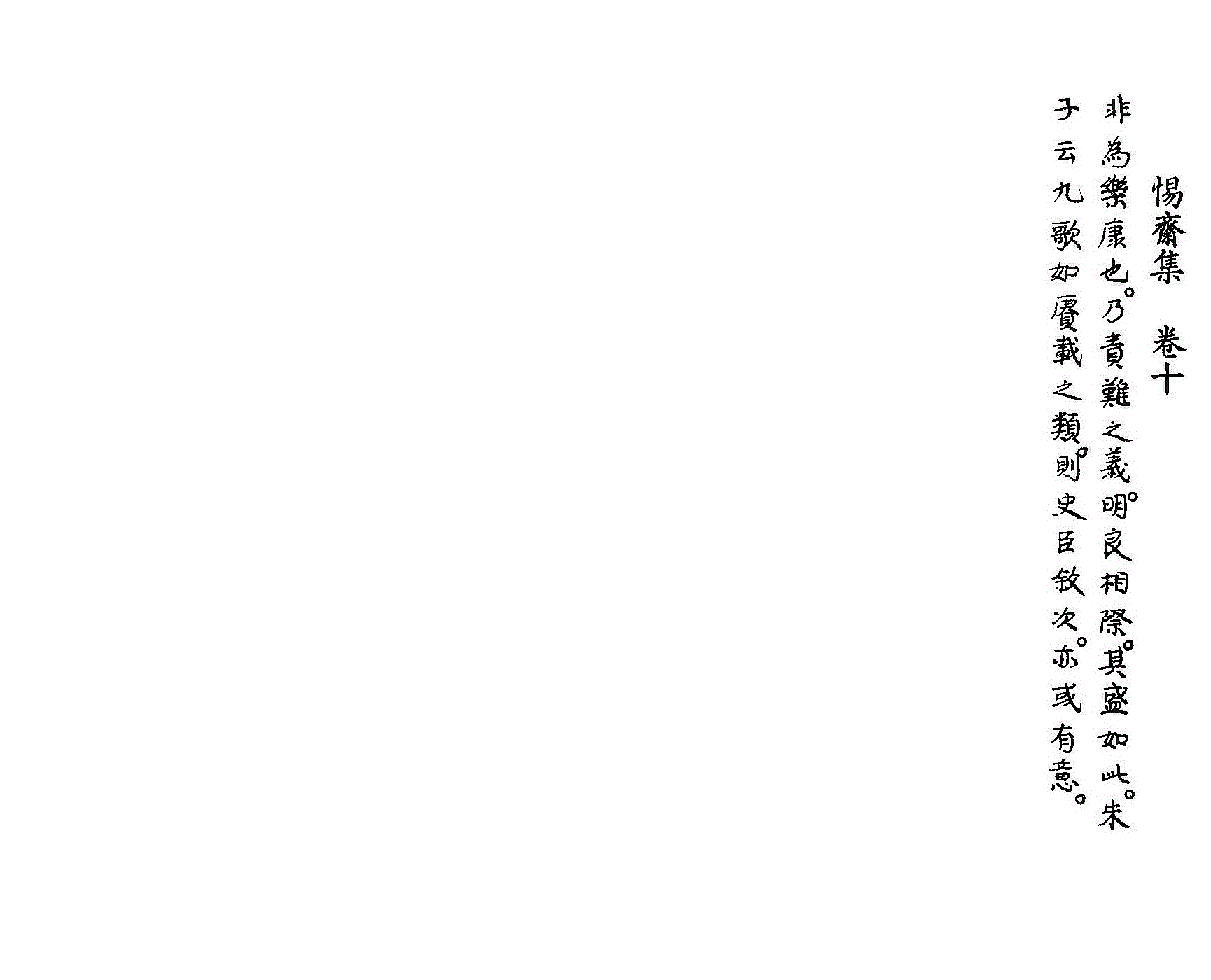 非为乐康也。乃责难之义。明良相际。其盛如此。朱子云九歌如赓载之类。则史臣叙次。亦或有意。
非为乐康也。乃责难之义。明良相际。其盛如此。朱子云九歌如赓载之类。则史臣叙次。亦或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