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x 页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杂著
杂著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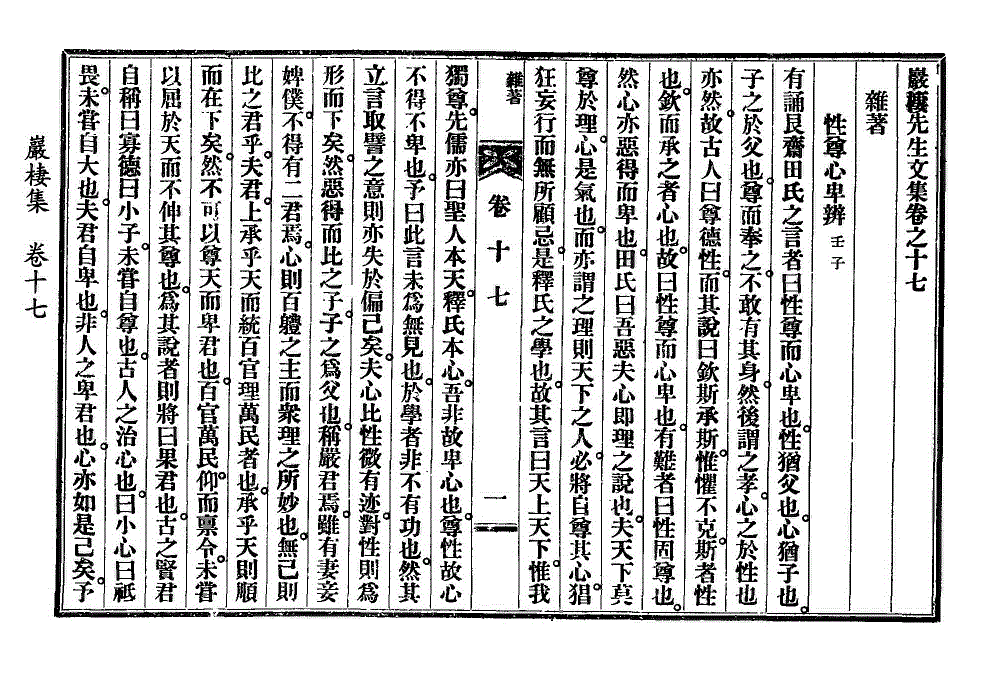 性尊心卑辨(壬子)
性尊心卑辨(壬子)有诵艮斋田氏之言者曰性尊而心卑也。性犹父也。心犹子也。子之于父也。尊而奉之。不敢有其身。然后谓之孝。心之于性也亦然。故古人曰尊德性。而其说曰钦斯承斯。惟惧不克。斯者性也。钦而承之者心也。故曰性尊而心卑也。有难者曰性固尊也。然心亦恶得而卑也。田氏曰吾恶夫心即理之说也。夫天下莫尊于理。心是气也。而亦谓之理则天下之人。必将自尊其心。猖狂妄行而无所顾忌。是释氏之学也。故其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先儒亦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吾非故卑心也。尊性故心不得不卑也。予曰此言未为无见也。于学者非不有功也。然其立言取譬之意则亦失于偏已矣。夫心比性微有迹。对性则为形而下矣。然恶得而比之子。子之为父也。称严君焉。虽有妻妾婢仆。不得有二君焉。心则百体之主而众理之所妙也。无已则比之君乎。夫君。上承乎天而统百官理万民者也。承乎天则顺而在下矣。然不可以尊天而卑君也。百官万民。仰而禀令。未尝以屈于天而不伸其尊也。为其说者则将曰果君也。古之贤君自称曰寡德曰小子。未尝自尊也。古人之治心也。曰小心曰祗畏。未尝自大也。夫君自卑也。非人之卑君也。心亦如是已矣。予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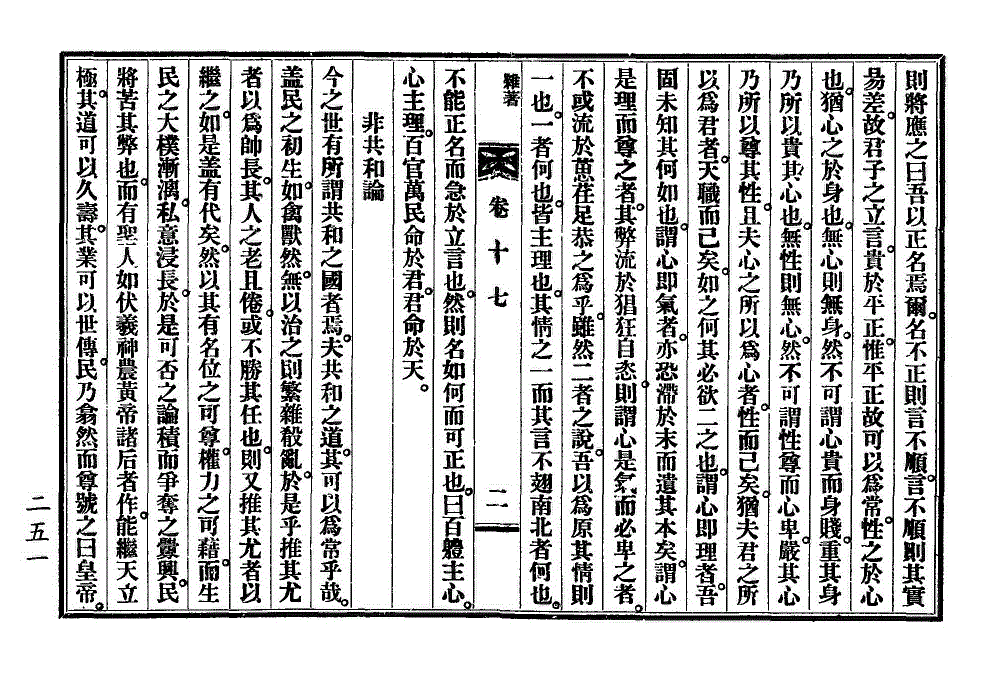 则将应之曰吾以正名焉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其实易差。故君子之立言。贵于平正。惟平正故可以为常。性之于心也。犹心之于身也。无心则无身。然不可谓心贵而身贱。重其身乃所以贵其心也。无性则无心。然不可谓性尊而心卑。严其心乃所以尊其性。且夫心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犹夫君之所以为君者。天职而已矣。如之何其必欲二之也。谓心即理者。吾固未知其何如也。谓心即气者。亦恐滞于末而遗其本矣。谓心是理而尊之者。其弊流于猖狂自恣。则谓心是气而必卑之者。不或流于葸荏足恭之为乎。虽然二者之说。吾以为原其情则一也。一者何也。皆主理也。其情之一而其言不翅南北者何也。不能正名而急于立言也。然则名如何而可正也。曰百体主心。心主理。百官万民命于君。君命于天。
则将应之曰吾以正名焉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其实易差。故君子之立言。贵于平正。惟平正故可以为常。性之于心也。犹心之于身也。无心则无身。然不可谓心贵而身贱。重其身乃所以贵其心也。无性则无心。然不可谓性尊而心卑。严其心乃所以尊其性。且夫心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犹夫君之所以为君者。天职而已矣。如之何其必欲二之也。谓心即理者。吾固未知其何如也。谓心即气者。亦恐滞于末而遗其本矣。谓心是理而尊之者。其弊流于猖狂自恣。则谓心是气而必卑之者。不或流于葸荏足恭之为乎。虽然二者之说。吾以为原其情则一也。一者何也。皆主理也。其情之一而其言不翅南北者何也。不能正名而急于立言也。然则名如何而可正也。曰百体主心。心主理。百官万民命于君。君命于天。非共和论
今之世有所谓共和之国者焉。夫共和之道。其可以为常乎哉。盖民之初生。如禽兽然。无以治之则繁杂殽乱。于是乎推其尤者以为帅长。其人之老且倦。或不胜其任也。则又推其尤者以继之。如是盖有代矣。然以其有名位之可尊。权力之可藉。而生民之大朴渐漓。私意浸长。于是可否之论积而争夺之衅兴。民将苦其弊也。而有圣人如伏羲神农黄帝诸后者作。能继天立极。其道可以久寿。其业可以世传。民乃翕然而尊号之曰皇帝。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2H 页
 奉事之以为君。承下之以为臣。及其没也而遗泽存。其嗣之贤也则世袭而不移。其不能也则民又去之而之他。夫其世袭与去而之他。非其民之所能为也天也。唐尧氏作。不得其嗣。于是相天下之士而有曰舜者。于是询之于臣。暴之于民。命之于神。既皆曰可。凡二十有八年。然后举天下而传之。其得之若此其难也。予之若此其审也。故孔子称之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舜又不得其嗣。于是相天下之士曰禹。以其道行之。天下无异心。后世无疑辞。夫尧舜之传贤。虞夏之受禅。非其君与臣之所能为也天也。自夏以后。世袭之道。未之或改也。改之则乱。故子哙惑焉而戮。汉献帝胁焉而亡。至其德之甚衰而民必去之。然后有伐而代之者。汤武是已。有乘乱而取之者。汉唐明是已。有非其欲而得之者。宋艺祖是已。然犹上者有惭德之说。下者有诡获之贬。秦晋以下无讥焉。若夫德可以代之。势可以取之。命可以得之。而犹且不敢有其心焉。终其身而不变者。文王是已。故孔子称之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君臣之义。犹父子之亲。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故文王之事纣也。尽其诚敬而已。不见其君之非也。天下之涂炭。非不隐于心也。而君臣之义。有大于此者。故不敢违也。是故在上则为文王。在下则为孔子。孔子之事君也。命召之则色勃如也。入其门则鞠躬如也。过其位则如不能言也。升其堂则如不能息也。其为礼也则曰过公门必
奉事之以为君。承下之以为臣。及其没也而遗泽存。其嗣之贤也则世袭而不移。其不能也则民又去之而之他。夫其世袭与去而之他。非其民之所能为也天也。唐尧氏作。不得其嗣。于是相天下之士而有曰舜者。于是询之于臣。暴之于民。命之于神。既皆曰可。凡二十有八年。然后举天下而传之。其得之若此其难也。予之若此其审也。故孔子称之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舜又不得其嗣。于是相天下之士曰禹。以其道行之。天下无异心。后世无疑辞。夫尧舜之传贤。虞夏之受禅。非其君与臣之所能为也天也。自夏以后。世袭之道。未之或改也。改之则乱。故子哙惑焉而戮。汉献帝胁焉而亡。至其德之甚衰而民必去之。然后有伐而代之者。汤武是已。有乘乱而取之者。汉唐明是已。有非其欲而得之者。宋艺祖是已。然犹上者有惭德之说。下者有诡获之贬。秦晋以下无讥焉。若夫德可以代之。势可以取之。命可以得之。而犹且不敢有其心焉。终其身而不变者。文王是已。故孔子称之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君臣之义。犹父子之亲。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故文王之事纣也。尽其诚敬而已。不见其君之非也。天下之涂炭。非不隐于心也。而君臣之义。有大于此者。故不敢违也。是故在上则为文王。在下则为孔子。孔子之事君也。命召之则色勃如也。入其门则鞠躬如也。过其位则如不能言也。升其堂则如不能息也。其为礼也则曰过公门必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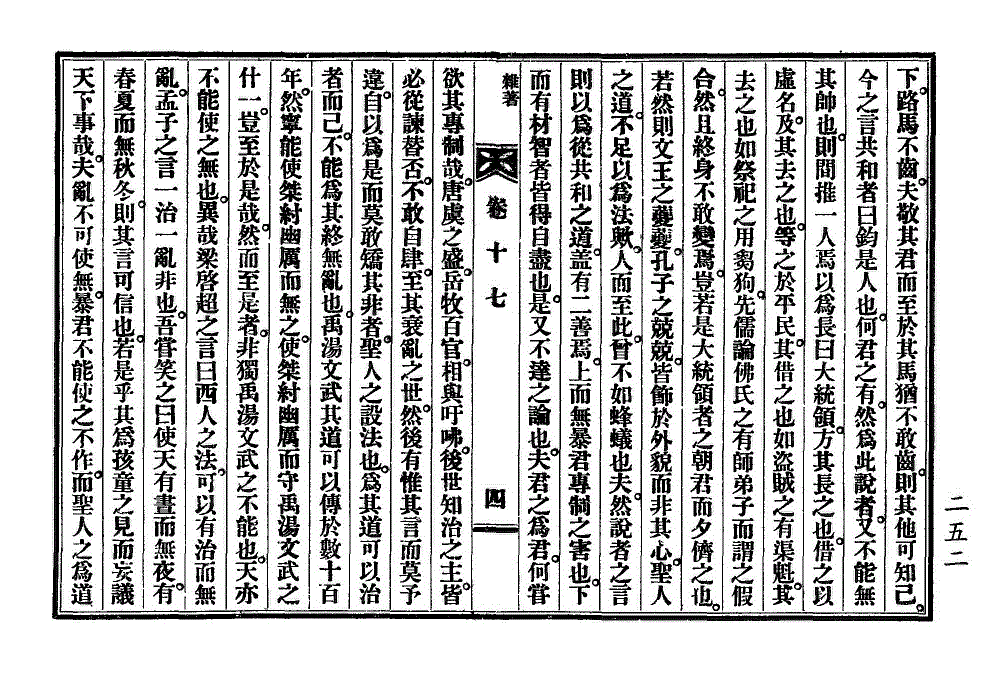 下。路马不齿。夫敬其君而至于其马犹不敢齿。则其他可知已。今之言共和者曰钧是人也。何君之有。然为此说者。又不能无其帅也。则间推一人焉以为长曰大统领。方其长之也。借之以虚名。及其去之也。等之于平民。其借之也如盗贼之有渠魁。其去之也如祭祀之用刍狗。先儒论佛氏之有师弟子而谓之假合。然且终身不敢变焉。岂若是大统领者之朝君而夕侪之也。若然则文王之夔夔。孔子之兢兢。皆饰于外貌而非其心。圣人之道。不足以为法欤。人而至此。曾不如蜂蚁也夫。然说者之言则以为从共和之道。盖有二善焉。上而无暴君专制之害也。下而有材智者皆得自尽也。是又不达之论也。夫君之为君。何尝欲其专制哉。唐虞之盛。岳牧百官。相与吁咈。后世知治之主。皆必从谏替否。不敢自肆。至其衰乱之世。然后有惟其言而莫予违。自以为是而莫敢矫其非者。圣人之设法也。为其道可以治者而已。不能为其终无乱也。禹汤文武其道可以传于数十百年。然宁能使桀纣幽厉而无之。使桀纣幽厉而守禹汤文武之什一。岂至于是哉。然而至是者。非独禹汤文武之不能也。天亦不能使之无也。异哉梁启超之言曰西人之法。可以有治而无乱。孟子之言一治一乱非也。吾尝笑之曰使天有昼而无夜。有春夏而无秋冬。则其言可信也。若是乎其为孩童之见而妄议天下事哉。夫乱不可使无。暴君不能使之不作。而圣人之为道
下。路马不齿。夫敬其君而至于其马犹不敢齿。则其他可知已。今之言共和者曰钧是人也。何君之有。然为此说者。又不能无其帅也。则间推一人焉以为长曰大统领。方其长之也。借之以虚名。及其去之也。等之于平民。其借之也如盗贼之有渠魁。其去之也如祭祀之用刍狗。先儒论佛氏之有师弟子而谓之假合。然且终身不敢变焉。岂若是大统领者之朝君而夕侪之也。若然则文王之夔夔。孔子之兢兢。皆饰于外貌而非其心。圣人之道。不足以为法欤。人而至此。曾不如蜂蚁也夫。然说者之言则以为从共和之道。盖有二善焉。上而无暴君专制之害也。下而有材智者皆得自尽也。是又不达之论也。夫君之为君。何尝欲其专制哉。唐虞之盛。岳牧百官。相与吁咈。后世知治之主。皆必从谏替否。不敢自肆。至其衰乱之世。然后有惟其言而莫予违。自以为是而莫敢矫其非者。圣人之设法也。为其道可以治者而已。不能为其终无乱也。禹汤文武其道可以传于数十百年。然宁能使桀纣幽厉而无之。使桀纣幽厉而守禹汤文武之什一。岂至于是哉。然而至是者。非独禹汤文武之不能也。天亦不能使之无也。异哉梁启超之言曰西人之法。可以有治而无乱。孟子之言一治一乱非也。吾尝笑之曰使天有昼而无夜。有春夏而无秋冬。则其言可信也。若是乎其为孩童之见而妄议天下事哉。夫乱不可使无。暴君不能使之不作。而圣人之为道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3H 页
 则有可以迟乱而弛暴者。贾谊所称三代之教太子其要也。人性不甚相远。桀纣幽厉岂世出之资哉。中材者可以与之上也。有其君则有其臣。人材之不足非所忧也。三代以下。教道不举。而教太子之法尤坏。故虽以汉文武之仁英而使其子博局而杀人。开博望苑而杂进宾客。其速乱而启暴。不亦宜哉。今欧美之为共和者。未及百年也。又其运之方升也。故其法犹可以支持。使如汉唐殷周之久也。则其法之召乱而兴暴。可以防也哉。夫人之有材智者。固欲其用之尽也。然世之兴也则材智之士毕显而尽其用。其衰也则有屈伏而不见用者矣。然不有用于显。必有施于隐。不有用于时。必有益于后。若人人而必欲其显而有用于时。理之所不能然也。且夫位有贵贱。任有大小。贵者令之。贱者承之。大者万之。小者一之。不敢相违越。斯之为治。今也使贱者加其贵。小者侵其大。嚣嚣然而议之。纷纷然而更之。名虽为治。其实则乱。夫乱之为名也。岂争夺相杀流离不相属之谓哉。孔子曰席而无上下。是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是乱于车也。推此言也。无贵贱无大小。是乱于国也已矣。恶睹其为治哉。故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也设院置员。使人人得以议之。又不得则各自为政党。演说以鼓之。新报以播之。求其更进。如积薪然。后者欲其为上也。如地蜂之起也。皆有螫人之心焉。谓之各尽其材智。不亦锐乎。且大材不
则有可以迟乱而弛暴者。贾谊所称三代之教太子其要也。人性不甚相远。桀纣幽厉岂世出之资哉。中材者可以与之上也。有其君则有其臣。人材之不足非所忧也。三代以下。教道不举。而教太子之法尤坏。故虽以汉文武之仁英而使其子博局而杀人。开博望苑而杂进宾客。其速乱而启暴。不亦宜哉。今欧美之为共和者。未及百年也。又其运之方升也。故其法犹可以支持。使如汉唐殷周之久也。则其法之召乱而兴暴。可以防也哉。夫人之有材智者。固欲其用之尽也。然世之兴也则材智之士毕显而尽其用。其衰也则有屈伏而不见用者矣。然不有用于显。必有施于隐。不有用于时。必有益于后。若人人而必欲其显而有用于时。理之所不能然也。且夫位有贵贱。任有大小。贵者令之。贱者承之。大者万之。小者一之。不敢相违越。斯之为治。今也使贱者加其贵。小者侵其大。嚣嚣然而议之。纷纷然而更之。名虽为治。其实则乱。夫乱之为名也。岂争夺相杀流离不相属之谓哉。孔子曰席而无上下。是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是乱于车也。推此言也。无贵贱无大小。是乱于国也已矣。恶睹其为治哉。故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也设院置员。使人人得以议之。又不得则各自为政党。演说以鼓之。新报以播之。求其更进。如积薪然。后者欲其为上也。如地蜂之起也。皆有螫人之心焉。谓之各尽其材智。不亦锐乎。且大材不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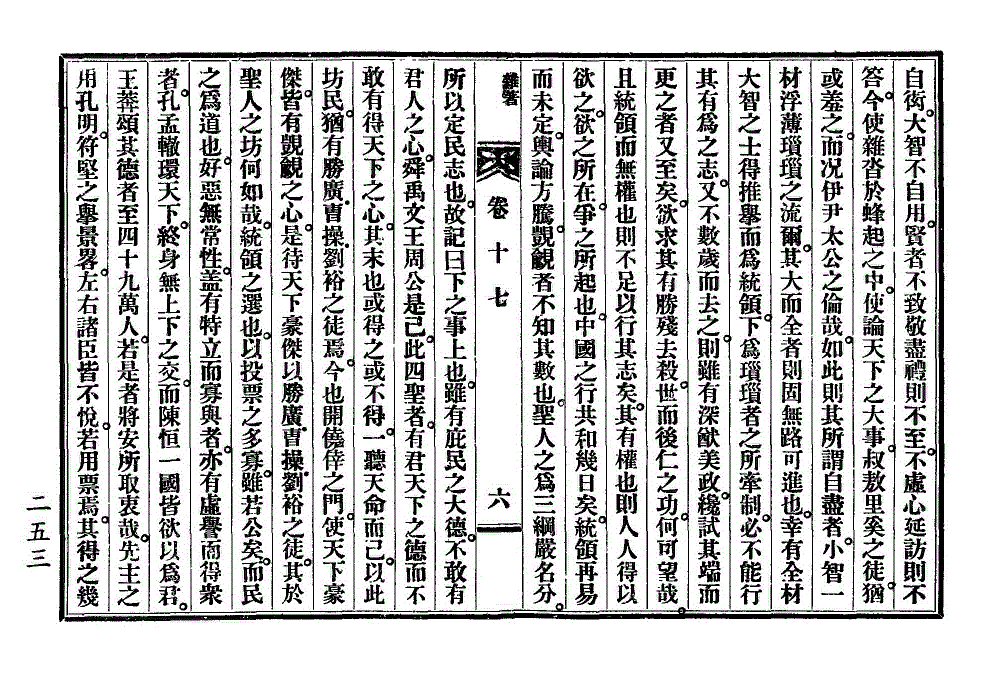 自衒。大智不自用。贤者不致敬尽礼则不至。不虚心延访则不答。今使杂沓于蜂起之中。使论天下之大事。叔敖里奚之徒。犹或羞之。而况伊尹太公之伦哉。如此则其所谓自尽者。小智一材浮薄琐琐之流尔。其大而全者则固无路可进也。幸有全材大智之士得推举而为统领。下为琐琐者之所牵制。必不能行其有为之志。又不数岁而去之。则虽有深猷美政。才试其端而更之者又至矣。欲求其有胜残去杀。世而后仁之功。何可望哉。且统领而无权也则不足以行其志矣。其有权也则人人得以欲之。欲之所在。争之所起也。中国之行共和几日矣。统领再易而未定。舆论方腾。觊觎者不知其数也。圣人之为三纲严名分。所以定民志也。故记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人之心。舜禹文王周公是已。此四圣者。有君天下之德而不敢有得天下之心。其末也或得之或不得。一听天命而已。以此坊民。犹有胜广,曹操,刘裕之徒焉。今也开侥倖之门。使天下豪杰。皆有觊觎之心。是待天下豪杰以胜广,曹操,刘裕之徒。其于圣人之坊何如哉。统领之选也。以投票之多寡。虽若公矣。而民之为道也。好恶无常性。盖有特立而寡与者。亦有虚誉而得众者。孔孟辙环天下。终身无上下之交。而陈恒一国皆欲以为君。王莽颂其德者至四十九万人。若是者将安所取衷哉。先主之用孔明。符坚之举景略。左右诸臣皆不悦。若用票焉。其得之几
自衒。大智不自用。贤者不致敬尽礼则不至。不虚心延访则不答。今使杂沓于蜂起之中。使论天下之大事。叔敖里奚之徒。犹或羞之。而况伊尹太公之伦哉。如此则其所谓自尽者。小智一材浮薄琐琐之流尔。其大而全者则固无路可进也。幸有全材大智之士得推举而为统领。下为琐琐者之所牵制。必不能行其有为之志。又不数岁而去之。则虽有深猷美政。才试其端而更之者又至矣。欲求其有胜残去杀。世而后仁之功。何可望哉。且统领而无权也则不足以行其志矣。其有权也则人人得以欲之。欲之所在。争之所起也。中国之行共和几日矣。统领再易而未定。舆论方腾。觊觎者不知其数也。圣人之为三纲严名分。所以定民志也。故记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人之心。舜禹文王周公是已。此四圣者。有君天下之德而不敢有得天下之心。其末也或得之或不得。一听天命而已。以此坊民。犹有胜广,曹操,刘裕之徒焉。今也开侥倖之门。使天下豪杰。皆有觊觎之心。是待天下豪杰以胜广,曹操,刘裕之徒。其于圣人之坊何如哉。统领之选也。以投票之多寡。虽若公矣。而民之为道也。好恶无常性。盖有特立而寡与者。亦有虚誉而得众者。孔孟辙环天下。终身无上下之交。而陈恒一国皆欲以为君。王莽颂其德者至四十九万人。若是者将安所取衷哉。先主之用孔明。符坚之举景略。左右诸臣皆不悦。若用票焉。其得之几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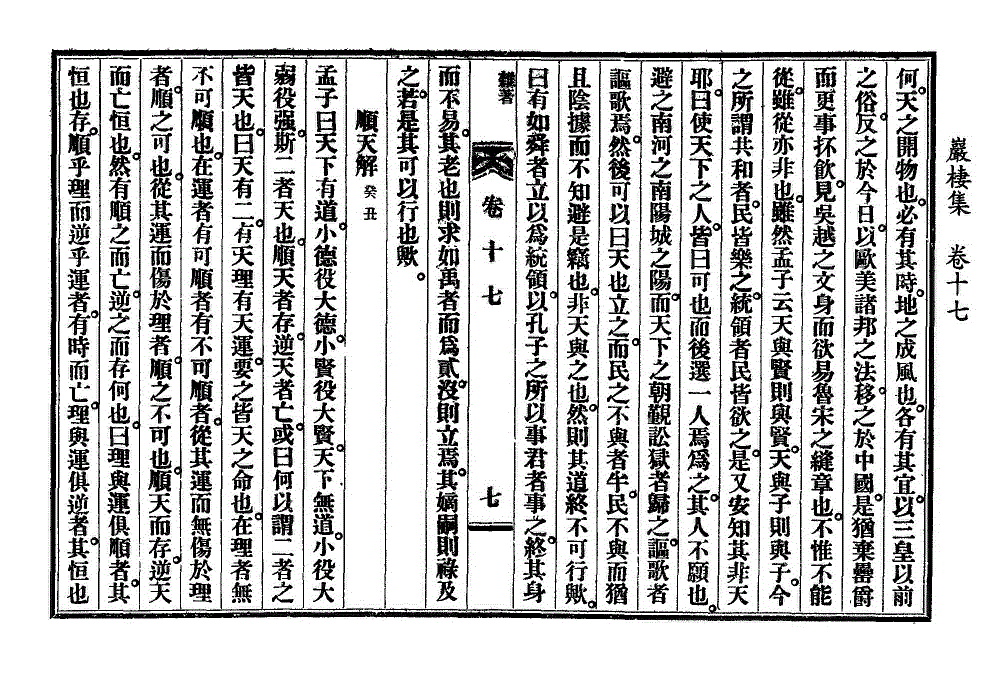 何。天之开物也。必有其时。地之成风也。各有其宜。以三皇以前之俗。反之于今日。以欧美诸邦之法。移之于中国。是犹弃罍爵而更事抔饮。见吴越之文身而欲易鲁宋之缝章也。不惟不能从。虽从亦非也。虽然孟子云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今之所谓共和者。民皆乐之。统领者民皆欲之。是又安知其非天耶。曰使天下之人。皆曰可也而后选一人焉为之。其人不愿也。避之南河之南阳城之阳。而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讴歌者讴歌焉。然后可以曰天也立之。而民之不与者半。民不与而犹且阴据而不知避是窃也。非天与之也。然则其道终不可行欤。曰有如舜者立以为统领。以孔子之所以事君者事之。终其身而不易。其老也则求如禹者而为贰。没则立焉。其嫡嗣则禄及之。若是其可以行也欤。
何。天之开物也。必有其时。地之成风也。各有其宜。以三皇以前之俗。反之于今日。以欧美诸邦之法。移之于中国。是犹弃罍爵而更事抔饮。见吴越之文身而欲易鲁宋之缝章也。不惟不能从。虽从亦非也。虽然孟子云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今之所谓共和者。民皆乐之。统领者民皆欲之。是又安知其非天耶。曰使天下之人。皆曰可也而后选一人焉为之。其人不愿也。避之南河之南阳城之阳。而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讴歌者讴歌焉。然后可以曰天也立之。而民之不与者半。民不与而犹且阴据而不知避是窃也。非天与之也。然则其道终不可行欤。曰有如舜者立以为统领。以孔子之所以事君者事之。终其身而不易。其老也则求如禹者而为贰。没则立焉。其嫡嗣则禄及之。若是其可以行也欤。顺天解(癸丑)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或曰何以谓二者之皆天也。曰天有二。有天理有天运。要之皆天之命也。在理者无不可顺也。在运者有可顺者有不可顺者。从其运而无伤于理者。顺之可也。从其运而伤于理者。顺之不可也。顺天而存。逆天而亡恒也。然有顺之而亡。逆之而存何也。曰理与运俱顺者。其恒也存。顺乎理而逆乎运者。有时而亡。理与运俱逆者。其恒也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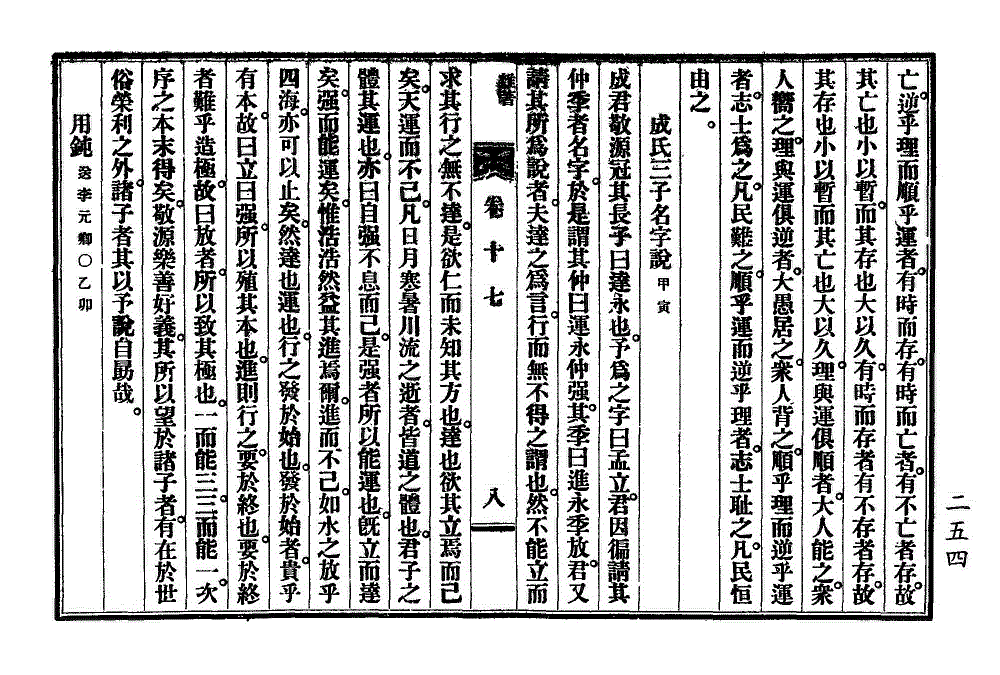 亡。逆乎理而顺乎运者。有时而存。有时而亡者。有不亡者存。故其亡也小以暂。而其存也大以久。有时而存者有不存者存。故其存也小以暂而其亡也大以久。理与运俱顺者。大人能之。众人向之。理与运俱逆者。大愚居之。众人背之。顺乎理而逆乎运者。志士为之。凡民难之。顺乎运而逆乎理者。志士耻之。凡民恒由之。
亡。逆乎理而顺乎运者。有时而存。有时而亡者。有不亡者存。故其亡也小以暂。而其存也大以久。有时而存者有不存者存。故其存也小以暂而其亡也大以久。理与运俱顺者。大人能之。众人向之。理与运俱逆者。大愚居之。众人背之。顺乎理而逆乎运者。志士为之。凡民难之。顺乎运而逆乎理者。志士耻之。凡民恒由之。成氏三子名字说(甲寅)
成君敬源冠其长子曰达永也。予为之字曰孟立。君因遍请其仲季者名字。于是谓其仲曰运永仲强。其季曰进永季放。君又请其所为说者。夫达之为言。行而无不得之谓也。然不能立而求其行之无不达。是欲仁而未知其方也。达也欲其立焉而已矣。天运而不已。凡日月寒暑川流之逝者。皆道之体也。君子之体其运也。亦曰自强不息而已。是强者所以能运也。既立而达矣。强而能运矣。惟浩浩然益其进焉尔。进而不已。如水之放乎四海。亦可以止矣。然达也运也。行之发于始也。发于始者。贵乎有本。故曰立曰强。所以殖其本也。进则行之。要于终也。要于终者难乎造极。故曰放者。所以致其极也。一而能三。三而能一。次序之本末得矣。敬源乐善好义。其所以望于诸子者。有在于世俗荣利之外。诸子者其以予说自勖哉。
用钝(送李元卿○乙卯)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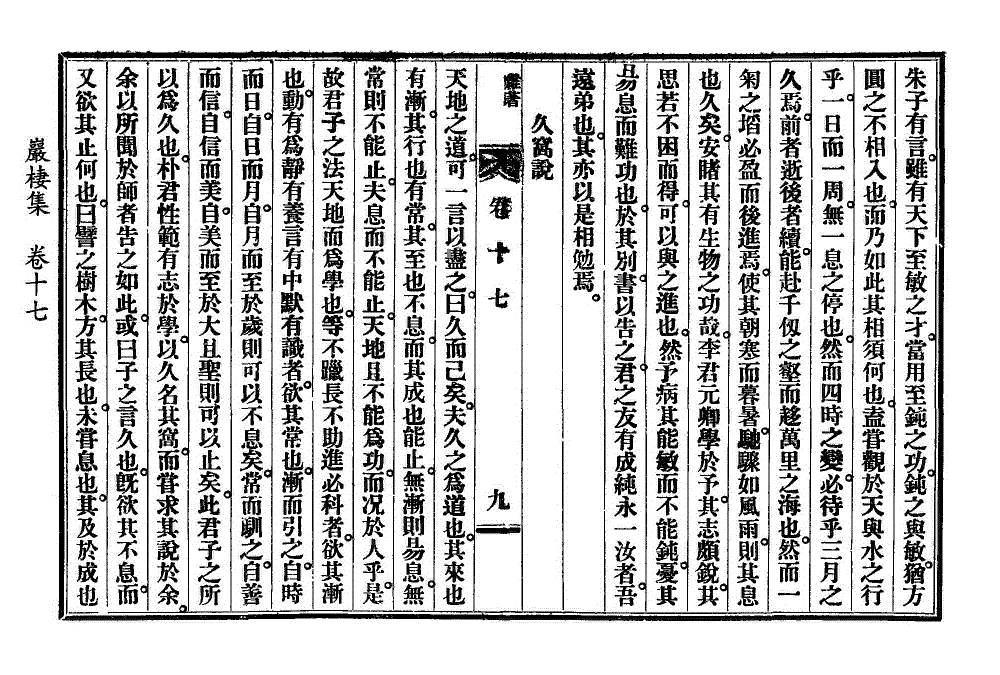 朱子有言。虽有天下至敏之才。当用至钝之功。钝之与敏。犹方圆之不相入也。而乃如此其相须何也。盍尝观于天与水之行乎。一日而一周。无一息之停也。然而四时之变。必待乎三月之久焉。前者逝后者续。能赴千仞之壑而趍万里之海也。然而一匊之埳必盈而后进焉。使其朝寒而暮暑。驰骤如风雨。则其息也久矣。安睹其有生物之功哉。李君元卿学于予。其志颇锐。其思若不困而得。可以与之进也。然予病其能敏而不能钝。忧其易息而难功也。于其别。书以告之。君之友有成纯永一汝者。吾远弟也。其亦以是相勉焉。
朱子有言。虽有天下至敏之才。当用至钝之功。钝之与敏。犹方圆之不相入也。而乃如此其相须何也。盍尝观于天与水之行乎。一日而一周。无一息之停也。然而四时之变。必待乎三月之久焉。前者逝后者续。能赴千仞之壑而趍万里之海也。然而一匊之埳必盈而后进焉。使其朝寒而暮暑。驰骤如风雨。则其息也久矣。安睹其有生物之功哉。李君元卿学于予。其志颇锐。其思若不困而得。可以与之进也。然予病其能敏而不能钝。忧其易息而难功也。于其别。书以告之。君之友有成纯永一汝者。吾远弟也。其亦以是相勉焉。久窝说
天地之道。可一言以尽之。曰久而已矣。夫久之为道也。其来也有渐。其行也有常。其至也不息。而其成也能止。无渐则易息。无常则不能止。夫息而不能止。天地且不能为功。而况于人乎。是故君子之法天地而为学也。等不躐长不助进必科者。欲其渐也。动有为静有养言有中默有识者。欲其常也。渐而引之。自时而日。自日而月。自月而至于岁则可以不息矣。常而驯之。自善而信。自信而美。自美而至于大且圣则可以止矣。此君子之所以为久也。朴君性范有志于学。以久名其窝。而尝求其说于余。余以所闻于师者告之如此。或曰子之言久也。既欲其不息。而又欲其止何也。曰譬之树木。方其长也。未尝息也。其及于成也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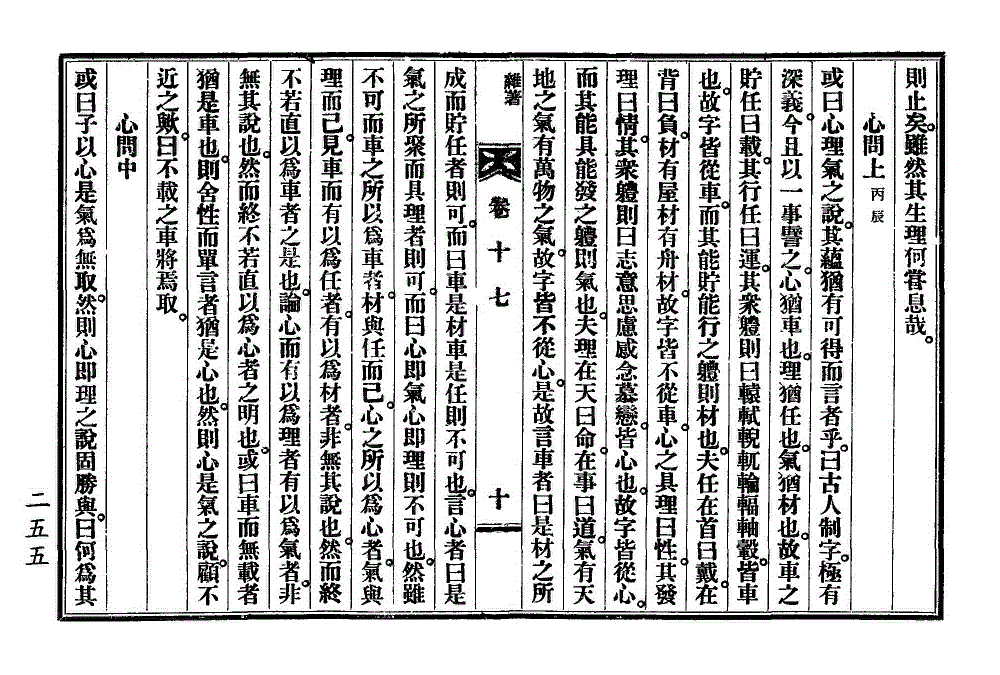 则止矣。虽然其生理何尝息哉。
则止矣。虽然其生理何尝息哉。心问上(丙辰)
或曰心理气之说。其蕴犹有可得而言者乎。曰古人制字。极有深义。今且以一事譬之。心犹车也。理犹任也。气犹材也。故车之贮任曰载。其行任曰运。其众体则曰辕轼輗軏轮辐轴毂。皆车也。故字皆从车。而其能贮能行之体则材也。夫任在首曰戴。在背曰负。材有屋材有舟材。故字皆不从车。心之具理曰性。其发理曰情。其众体则曰志意思虑感念慕恋。皆心也。故字皆从心。而其能具能发之体则气也。夫理在天曰命。在事曰道。气有天地之气有万物之气。故字皆不从心。是故言车者曰是材之所成而贮任者则可。而曰车是材车是任则不可也。言心者曰是气之所聚而具理者则可。而曰心即气心即理则不可也。然虽不可而车之所以为车者。材与任而已。心之所以为心者。气与理而已。见车而有以为任者。有以为材者。非无其说也。然而终不若直以为车者之是也。论心而有以为理者有以为气者。非无其说也。然而终不若直以为心者之明也。或曰车而无载者犹是车也。则舍性而单言者犹是心也。然则心是气之说。顾不近之欤。曰不载之车将焉取。
心问中
或曰子以心是气为无取。然则心即理之说固胜与。曰何为其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6H 页
 胜也。心即理之说。其犹告子之生之谓性乎。孔子言气质之性则生固未始非性也。然而语性之本体则远矣。孟子言仁义之心则理固未始非心也。然而语心之实相则疏矣。告子论性而失之抑。今之人论心而失之抗。其不中一也。然抑者不及也。犹可进也。抗而至于过则一往而不可反矣。其为失顾不大与。夫告子之言。未为无所出也。而孟子诘之而不能答。非无以答也。自知其不安也。使孟子而在。必将语今之人曰理则尧与蹠与涂人一与。则将曰然。然则蹠之心犹尧之心。尧之心犹涂人之心与。则吾未知今之人。将何以答之与。
胜也。心即理之说。其犹告子之生之谓性乎。孔子言气质之性则生固未始非性也。然而语性之本体则远矣。孟子言仁义之心则理固未始非心也。然而语心之实相则疏矣。告子论性而失之抑。今之人论心而失之抗。其不中一也。然抑者不及也。犹可进也。抗而至于过则一往而不可反矣。其为失顾不大与。夫告子之言。未为无所出也。而孟子诘之而不能答。非无以答也。自知其不安也。使孟子而在。必将语今之人曰理则尧与蹠与涂人一与。则将曰然。然则蹠之心犹尧之心。尧之心犹涂人之心与。则吾未知今之人。将何以答之与。心问下
或曰然则心将恶乎名而可。曰是理气之合而得名者也。曰此先儒之说也而子从之。与抑别有见与。曰奚独先儒之云然。但据乎今人之所论而亦可知也已。夫同一论心也。而有以为气者。有以为理者。以为气者。是见其气也者。以为理者。是见其理也者。即此而二者之均有可知。于此有物焉。或以为白。或以为黑。以为白者是见其白也者。以为黑者是见其黑也者。即此而白黑之两在可知。特见者自执其一而矜言之尔。虽然合理气之说完矣。而犹未若非理非气而直谓之心之确也。盖物有合数端而成者。其名既变则其故可无辨。辨之不已则多言而阔略于事。譬如说粥然。或曰米也。或曰水也。是见其一而不知其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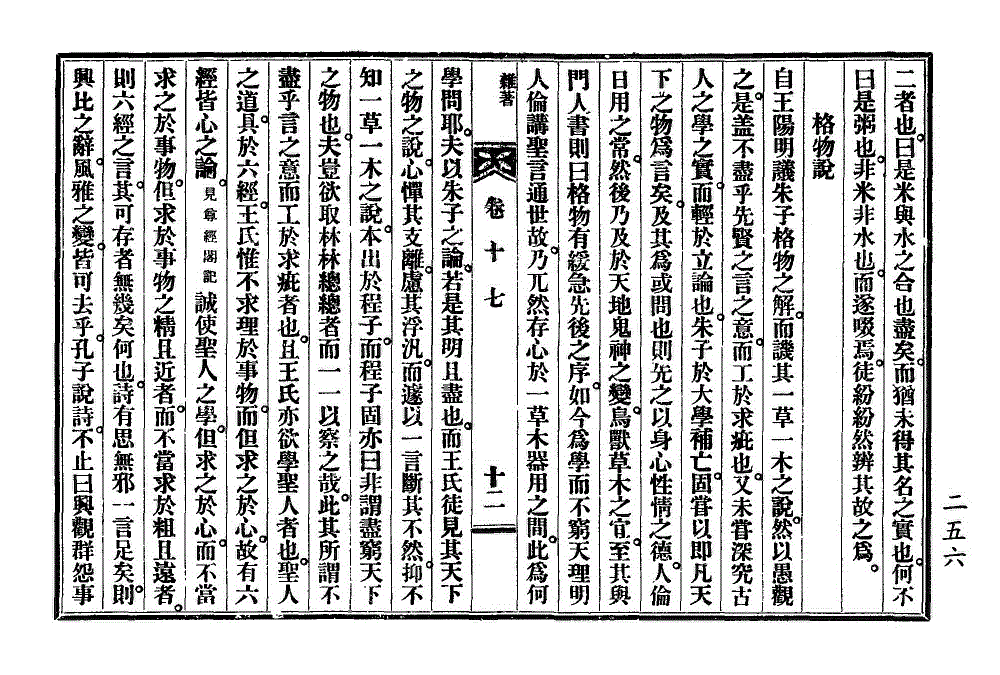 二者也。曰是米与水之合也尽矣。而犹未得其名之实也。何不曰是粥也。非米非水也。而遂啜焉。徒纷纷然辨其故之为。
二者也。曰是米与水之合也尽矣。而犹未得其名之实也。何不曰是粥也。非米非水也。而遂啜焉。徒纷纷然辨其故之为。格物说
自王阳明议朱子格物之解。而讥其一草一木之说。然以愚观之。是盖不尽乎先贤之言之意。而工于求疵也。又未尝深究古人之学之实。而轻于立论也。朱子于大学补亡。固尝以即凡天下之物为言矣。及其为或问也则先之以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然后乃及于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至其与门人书则曰格物有缓急先后之序。如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此为何学问耶。夫以朱子之论。若是其明且尽也。而王氏徒见其天下之物之说。心惮其支离。虑其浮汎。而遽以一言断其不然。抑不知一草一木之说。本出于程子。而程子固亦曰非谓尽穷天下之物也。夫岂欲取林林总总者而一一以察之哉。此其所谓不尽乎言之意而工于求疵者也。且王氏亦欲学圣人者也。圣人之道。具于六经。王氏惟不求理于事物。而但求之于心。故有六经皆心之论。(见尊经阁记)诚使圣人之学。但求之于心。而不当求之于事物。但求于事物之精且近者。而不当求于粗且远者。则六经之言。其可存者无几矣何也。诗有思无邪一言足矣。则兴比之辞。风雅之变。皆可去乎。孔子说诗。不止曰兴观群怨事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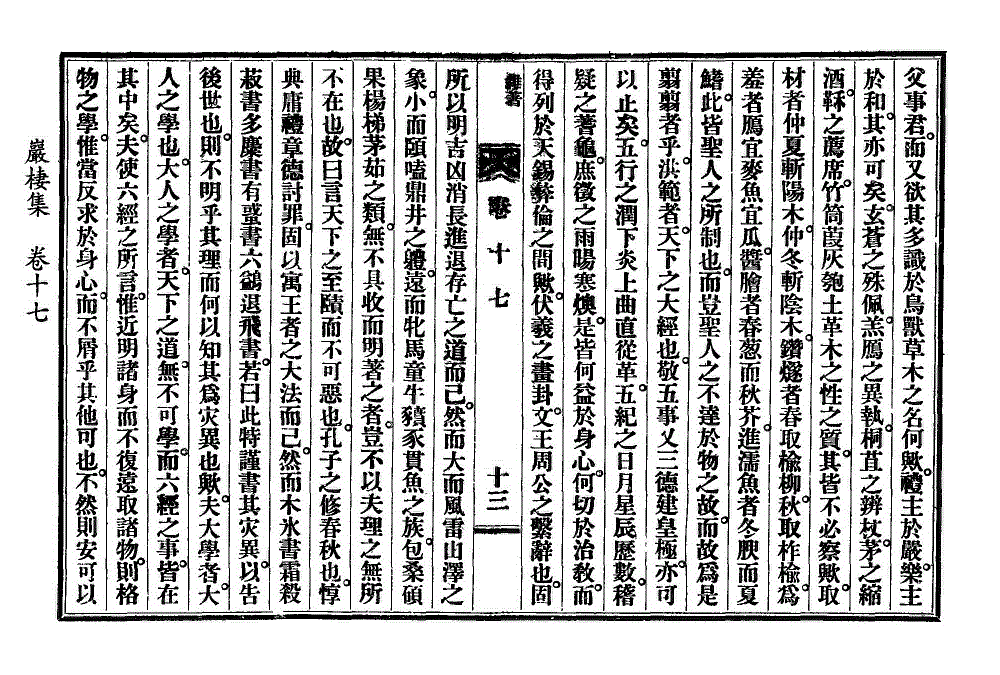 父事君。而又欲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欤。礼主于严。乐主于和。其亦可矣。玄苍之殊佩。羔雁之异执。桐苴之辨杖。茅之缩酒。秸之荐席。竹筒葭灰匏土革木之性之质。其皆不必察欤。取材者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钻燧者春取榆柳。秋取柞榆。为羞者雁宜麦鱼宜瓜。酱脍者春葱而秋芥。进濡鱼者冬腴而夏鳍。此皆圣人之所制也。而岂圣人之不达于物之故。而故为是剪剪者乎。洪范者。天下之大经也。敬五事乂三德建皇极。亦可以止矣。五行之润下炎上曲直从革。五纪之日月星辰历数。稽疑之蓍龟。庶徵之雨晹寒燠。是皆何益于身心。何切于治教。而得列于天锡彝伦之间欤。伏羲之画卦。文王周公之系辞也。固所以明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之道而已。然而大而风雷山泽之象。小而颐嗑鼎井之体。远而牝马童牛豮豕贯鱼之族。包桑硕果杨梯茅茹之类。无不具收而明著之者。岂不以夫理之无所不在也。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孔子之修春秋也。惇典庸礼章德讨罪。固以寓王者之大法而已。然而木冰书霜杀菽书多麋书有𧌒书六鹢退飞书。若曰此特谨书其灾异。以告后世也。则不明乎其理而何以知其为灾异也欤。夫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之学者。天下之道。无不可学。而六经之事。皆在其中矣。夫使六经之所言。惟近明诸身而不复远取诸物。则格物之学。惟当反求于身心。而不屑乎其他可也。不然则安可以
父事君。而又欲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何欤。礼主于严。乐主于和。其亦可矣。玄苍之殊佩。羔雁之异执。桐苴之辨杖。茅之缩酒。秸之荐席。竹筒葭灰匏土革木之性之质。其皆不必察欤。取材者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钻燧者春取榆柳。秋取柞榆。为羞者雁宜麦鱼宜瓜。酱脍者春葱而秋芥。进濡鱼者冬腴而夏鳍。此皆圣人之所制也。而岂圣人之不达于物之故。而故为是剪剪者乎。洪范者。天下之大经也。敬五事乂三德建皇极。亦可以止矣。五行之润下炎上曲直从革。五纪之日月星辰历数。稽疑之蓍龟。庶徵之雨晹寒燠。是皆何益于身心。何切于治教。而得列于天锡彝伦之间欤。伏羲之画卦。文王周公之系辞也。固所以明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之道而已。然而大而风雷山泽之象。小而颐嗑鼎井之体。远而牝马童牛豮豕贯鱼之族。包桑硕果杨梯茅茹之类。无不具收而明著之者。岂不以夫理之无所不在也。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孔子之修春秋也。惇典庸礼章德讨罪。固以寓王者之大法而已。然而木冰书霜杀菽书多麋书有𧌒书六鹢退飞书。若曰此特谨书其灾异。以告后世也。则不明乎其理而何以知其为灾异也欤。夫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之学者。天下之道。无不可学。而六经之事。皆在其中矣。夫使六经之所言。惟近明诸身而不复远取诸物。则格物之学。惟当反求于身心。而不屑乎其他可也。不然则安可以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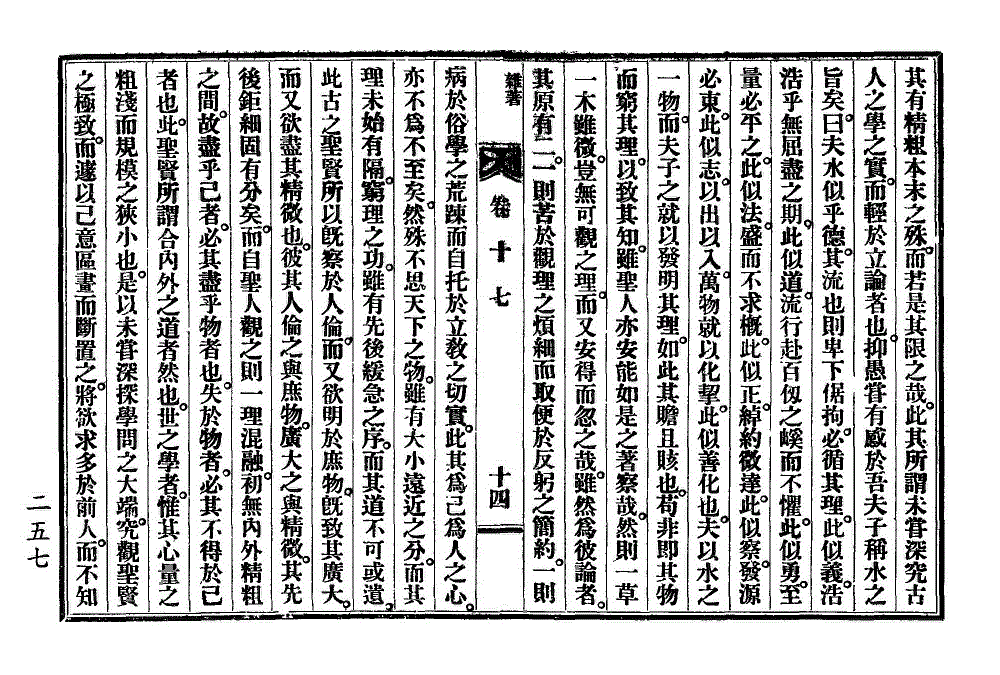 其有精粗本末之殊。而若是其限之哉。此其所谓未尝深究古人之学之实。而轻于立论者也。抑愚尝有感于吾夫子称水之旨矣。曰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挈。此似善化也。夫以水之一物。而夫子之就以发明其理。如此其赡且赅也。苟非即其物而穷其理。以致其知。虽圣人亦安能如是之著察哉。然则一草一木虽微。岂无可观之理。而又安得而忽之哉。虽然为彼论者。其原有二。一则苦于观理之烦细而取便于反躬之简约。一则病于俗学之荒疏而自托于立教之切实。此其为己为人之心。亦不为不至矣。然殊不思天下之物。虽有大小远近之分。而其理未始有隔。穷理之功。虽有先后缓急之序。而其道不可或遗。此古之圣贤所以既察于人伦。而又欲明于庶物。既致其广大。而又欲尽其精微也。彼其人伦之与庶物。广大之与精微。其先后钜细固有分矣。而自圣人观之则一理混融。初无内外精粗之间。故尽乎已者。必其尽乎物者也。失于物者。必其不得于己者也。此圣贤所谓合内外之道者然也。世之学者。惟其心量之粗浅而规模之狭小也。是以未尝深探学问之大端。究观圣贤之极致。而遽以己意区画而断置之。将欲求多于前人。而不知
其有精粗本末之殊。而若是其限之哉。此其所谓未尝深究古人之学之实。而轻于立论者也。抑愚尝有感于吾夫子称水之旨矣。曰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挈。此似善化也。夫以水之一物。而夫子之就以发明其理。如此其赡且赅也。苟非即其物而穷其理。以致其知。虽圣人亦安能如是之著察哉。然则一草一木虽微。岂无可观之理。而又安得而忽之哉。虽然为彼论者。其原有二。一则苦于观理之烦细而取便于反躬之简约。一则病于俗学之荒疏而自托于立教之切实。此其为己为人之心。亦不为不至矣。然殊不思天下之物。虽有大小远近之分。而其理未始有隔。穷理之功。虽有先后缓急之序。而其道不可或遗。此古之圣贤所以既察于人伦。而又欲明于庶物。既致其广大。而又欲尽其精微也。彼其人伦之与庶物。广大之与精微。其先后钜细固有分矣。而自圣人观之则一理混融。初无内外精粗之间。故尽乎已者。必其尽乎物者也。失于物者。必其不得于己者也。此圣贤所谓合内外之道者然也。世之学者。惟其心量之粗浅而规模之狭小也。是以未尝深探学问之大端。究观圣贤之极致。而遽以己意区画而断置之。将欲求多于前人。而不知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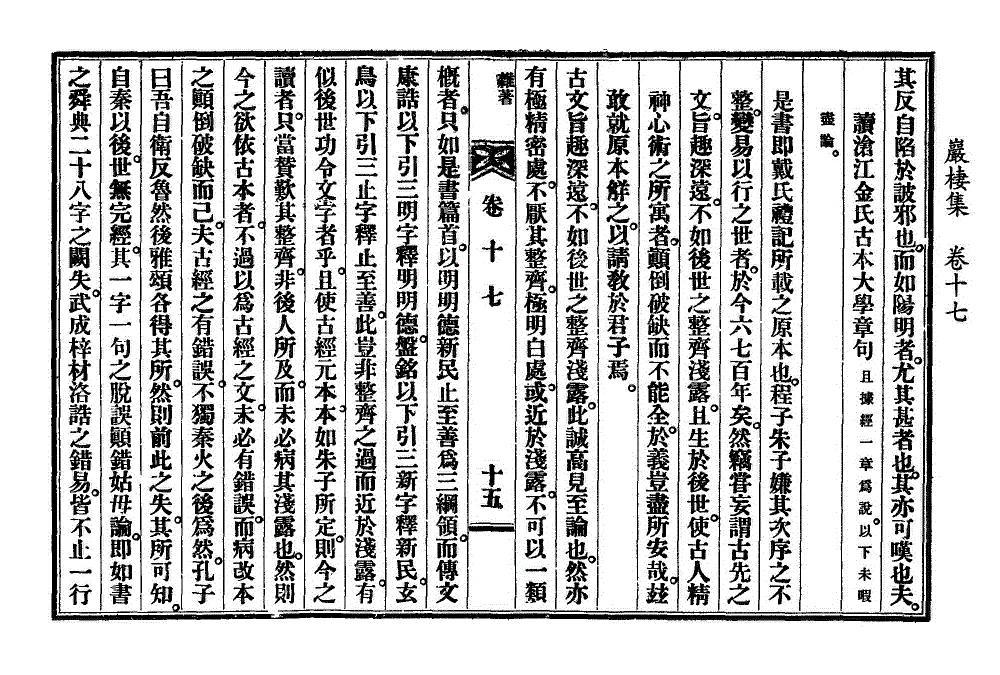 其反自陷于诐邪也。而如阳明者。尤其甚者也。其亦可叹也夫。
其反自陷于诐邪也。而如阳明者。尤其甚者也。其亦可叹也夫。读沧江金氏古本大学章句(且据经一章为说。以下未暇尽论。)
是书即戴氏礼记所载之原本也。程子朱子嫌其次序之不整。变易以行之世者。于今六七百年矣。然窃尝妄谓古先之文。旨趣深远。不如后世之整齐浅露。且生于后世。使古人精神心术之所寓者。颠倒破缺而不能全。于义岂尽所安哉。兹敢就原本解之。以请教于君子焉。
古文旨趣深远。不如后世之整齐浅露。此诚高见至论也。然亦有极精密处。不厌其整齐。极明白处。或近于浅露。不可以一类概者。只如是书篇首。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为三纲领。而传文康诰以下引三明字释明明德。盘铭以下引三新字释新民。玄鸟以下引三止字释止至善。此岂非整齐之过而近于浅露。有似后世功令文字者乎。且使古经元本。本如朱子所定。则今之读者。只当赞叹其整齐。非后人所及。而未必病其浅露也。然则今之欲依古本者。不过以为古经之文。未必有错误。而病改本之颠倒破缺而已。夫古经之有错误。不独秦火之后为然。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前此之失。其所可知。自秦以后。世无完经。其一字一句之脱误颠错姑毋论。即如书之舜典二十八字之阙失。武成梓材洛诰之错易。皆不止一行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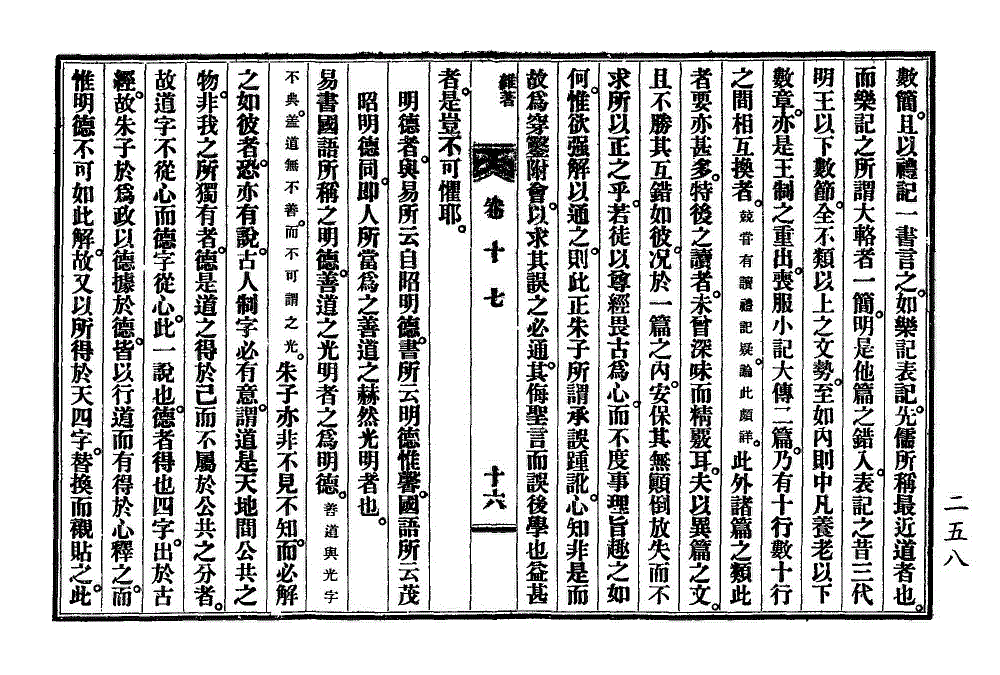 数简。且以礼记一书言之。如乐记表记。先儒所称最近道者也。而乐记之所谓大辂者一简。明是他篇之错入。表记之昔三代明王以下数节。全不类以上之文势。至如内则中凡养老以下数章。亦是王制之重出。丧服小记大传二篇。乃有十行数十行之间相互换者。(兢尝有读礼记疑。论此颇详。)此外诸篇之类此者要亦甚多。特后之读者。未曾深味而精覈耳。夫以异篇之文。且不胜其互错如彼。况于一篇之内。安保其无颠倒放失而不求所以正之乎。若徒以尊经畏古为心。而不度事理旨趣之如何。惟欲强解以通之。则此正朱子所谓承误踵讹。心知非是而故为穿凿附会。以求其误之必通。其侮圣言而误后学也益甚者。是岂不可惧耶。
数简。且以礼记一书言之。如乐记表记。先儒所称最近道者也。而乐记之所谓大辂者一简。明是他篇之错入。表记之昔三代明王以下数节。全不类以上之文势。至如内则中凡养老以下数章。亦是王制之重出。丧服小记大传二篇。乃有十行数十行之间相互换者。(兢尝有读礼记疑。论此颇详。)此外诸篇之类此者要亦甚多。特后之读者。未曾深味而精覈耳。夫以异篇之文。且不胜其互错如彼。况于一篇之内。安保其无颠倒放失而不求所以正之乎。若徒以尊经畏古为心。而不度事理旨趣之如何。惟欲强解以通之。则此正朱子所谓承误踵讹。心知非是而故为穿凿附会。以求其误之必通。其侮圣言而误后学也益甚者。是岂不可惧耶。明德者。与易所云自昭明德。书所云明德惟馨。国语所云茂昭明德同。即人所当为之善道之赫然光明者也。
易书国语所称之明德。善道之光明者之为明德。(善道与光字不典。盖道无不善。而不可谓之光。)朱子亦非不见不知。而必解之如彼者。恐亦有说。古人制字必有意。谓道是天地间公共之物。非我之所独有者。德是道之得于己而不属于公共之分者。故道字不从心而德字从心。此一说也。德者得也四字。出于古经。故朱子于为政以德据于德。皆以行道而有得于心释之。而惟明德不可如此解。故又以所得于天四字。替换而衬贴之。此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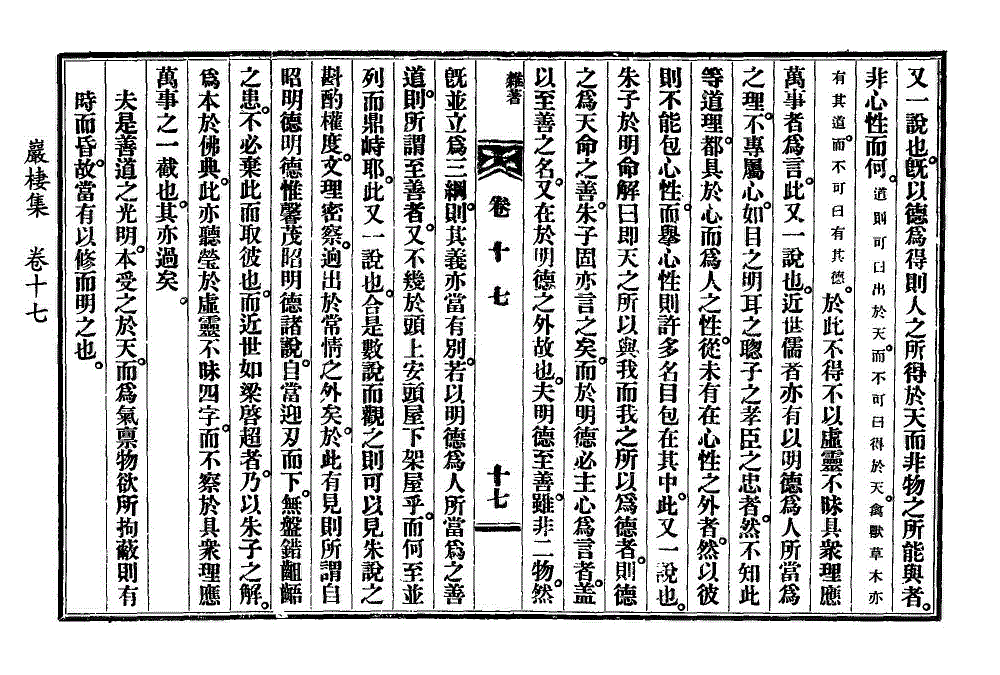 又一说也。既以德为得则人之所得于天而非物之所能与者。非心性而何。(道则可曰出于天。而不可曰得于天。禽兽草木亦有其道。而不可曰有其德。)于此不得不以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者为言。此又一说也。近世儒者亦有以明德为人所当为之理。不专属心。如目之明耳之聪子之孝臣之忠者。然不知此等道理。都具于心而为人之性。从未有在心性之外者。然以彼则不能包心性。而举心性则许多名目包在其中。此又一说也。朱子于明命解曰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则德之为天命之善。朱子固亦言之矣。而于明德必主心为言者。盖以至善之名。又在于明德之外故也。夫明德至善。虽非二物。然既并立为三纲。则其义亦当有别。若以明德为人所当为之善道。则所谓至善者。又不几于头上安头屋下架屋乎。而何至并列而鼎峙耶。此又一说也。合是数说而观之则可以见朱说之斟酌权度。文理密察。迥出于常情之外矣。于此有见则所谓自昭明德明德惟馨茂昭明德诸说。自当迎刃而下。无盘错龃龉之患。不必弃此而取彼也。而近世如梁启超者。乃以朱子之解。为本于佛典。此亦听莹于虚灵不昧四字。而不察于具众理应万事之一截也。其亦过矣。
又一说也。既以德为得则人之所得于天而非物之所能与者。非心性而何。(道则可曰出于天。而不可曰得于天。禽兽草木亦有其道。而不可曰有其德。)于此不得不以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者为言。此又一说也。近世儒者亦有以明德为人所当为之理。不专属心。如目之明耳之聪子之孝臣之忠者。然不知此等道理。都具于心而为人之性。从未有在心性之外者。然以彼则不能包心性。而举心性则许多名目包在其中。此又一说也。朱子于明命解曰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则德之为天命之善。朱子固亦言之矣。而于明德必主心为言者。盖以至善之名。又在于明德之外故也。夫明德至善。虽非二物。然既并立为三纲。则其义亦当有别。若以明德为人所当为之善道。则所谓至善者。又不几于头上安头屋下架屋乎。而何至并列而鼎峙耶。此又一说也。合是数说而观之则可以见朱说之斟酌权度。文理密察。迥出于常情之外矣。于此有见则所谓自昭明德明德惟馨茂昭明德诸说。自当迎刃而下。无盘错龃龉之患。不必弃此而取彼也。而近世如梁启超者。乃以朱子之解。为本于佛典。此亦听莹于虚灵不昧四字。而不察于具众理应万事之一截也。其亦过矣。夫是善道之光明。本受之于天。而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修而明之也。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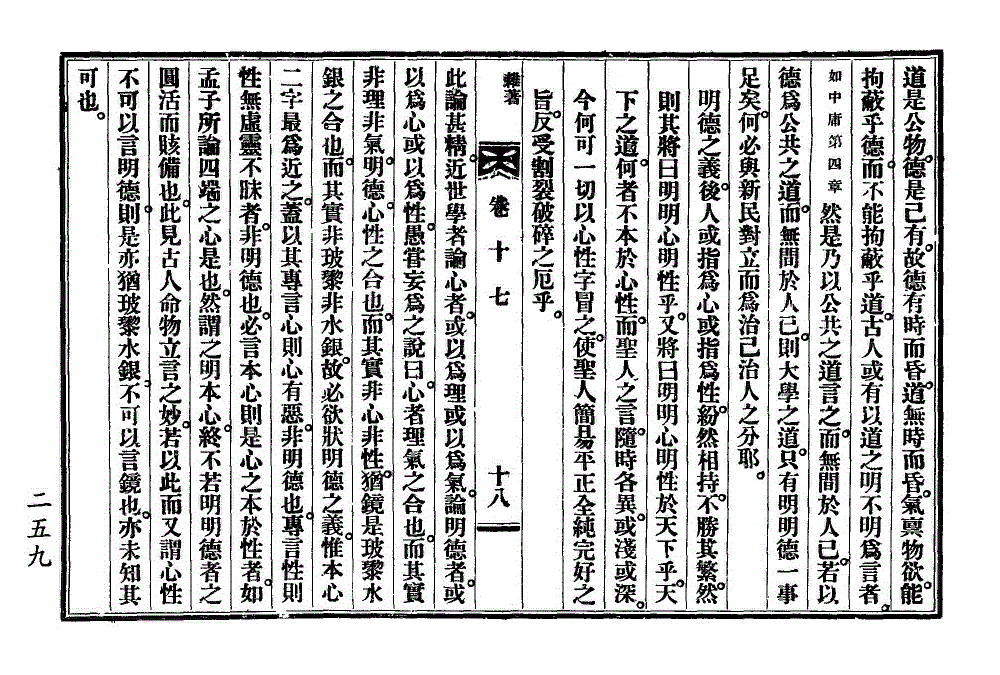 道是公物。德是己有。故德有时而昏。道无时而昏。气禀物欲。能拘蔽乎德。而不能拘蔽乎道。古人或有以道之明不明为言者。(如中庸第四章)然是乃以公共之道言之。而无间于人己。若以德为公共之道。而无间于人己。则大学之道。只有明明德一事足矣。何必与新民对立而为治己治人之分耶。
道是公物。德是己有。故德有时而昏。道无时而昏。气禀物欲。能拘蔽乎德。而不能拘蔽乎道。古人或有以道之明不明为言者。(如中庸第四章)然是乃以公共之道言之。而无间于人己。若以德为公共之道。而无间于人己。则大学之道。只有明明德一事足矣。何必与新民对立而为治己治人之分耶。明德之义。后人或指为心或指为性。纷然相持。不胜其繁。然则其将曰明明心明性乎。又将曰明明心明性于天下乎。天下之道。何者不本于心性。而圣人之言。随时各异。或浅或深。今何可一切以心性字冒之。使圣人简易平正全纯完好之旨。反受割裂破碎之厄乎。
此论甚精。近世学者论心者。或以为理或以为气。论明德者。或以为心或以为性。愚尝妄为之说曰。心者理气之合也。而其实非理非气。明德。心性之合也。而其实非心非性。犹镜是玻瓈水银之合也。而其实非玻瓈非水银。故必欲状明德之义。惟本心二字最为近之。盖以其专言心则心有恶。非明德也。专言性则性无虚灵不昧者。非明德也。必言本心则是心之本于性者。如孟子所论四端之心是也。然谓之明本心。终不若明明德者之圆活而赅备也。此见古人命物立言之妙。若以此而又谓心性不可以言明德。则是亦犹玻瓈水银。不可以言镜也。亦未知其可也。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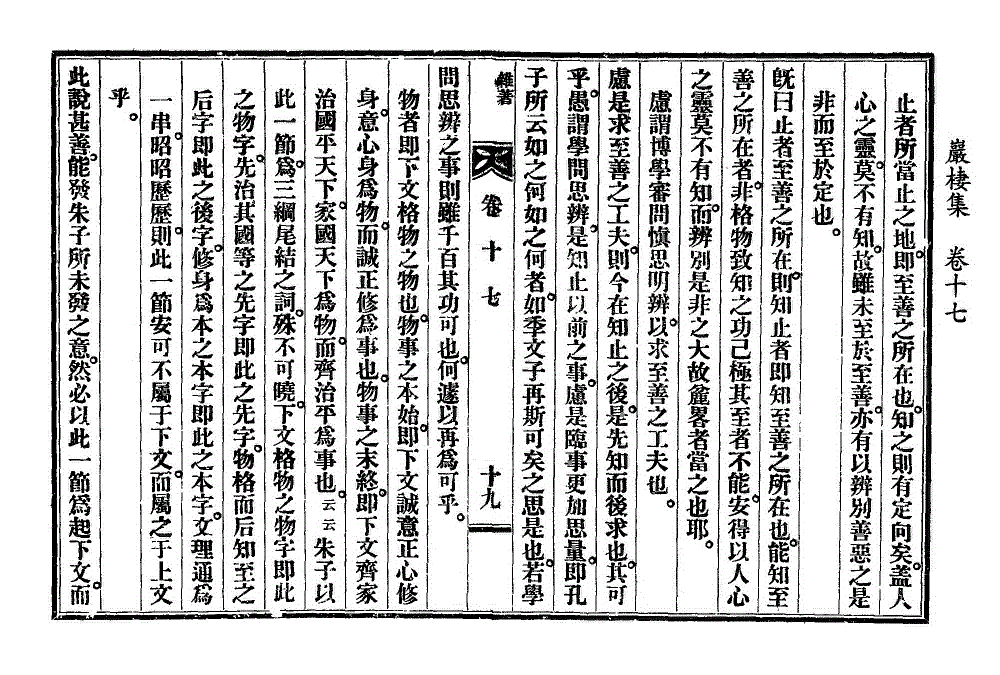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有定向矣。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故虽未至于至善。亦有以辨别善恶之是非而至于定也。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有定向矣。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故虽未至于至善。亦有以辨别善恶之是非而至于定也。既曰止者至善之所在。则知止者即知至善之所在也。能知至善之所在者。非格物致知之功已极其至者不能。安得以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辨别是非之大故粗略者当之也耶。
虑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至善之工夫也。
虑是求至善之工夫。则今在知止之后。是先知而后求也。其可乎。愚谓学问思辨。是知止以前之事。虑是临事更加思量。即孔子所云如之何如之何者。如季文子再斯可矣之思是也。若学问思辨之事则虽千百其功可也。何遽以再为可乎。
物者即下文格物之物也。物事之本始。即下文诚意正心修身。意心身为物。而诚正修为事也。物事之末终。即下文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为物。而齐治平为事也。(云云)朱子以此一节。为三纲尾结之词。殊不可晓。下文格物之物字即此之物字。先治其国等之先字即此之先字。物格而后知至之后字即此之后字。修身为本之本字即此之本字。文理通为一串。昭昭历历。则此一节安可不属于下文。而属之于上文乎。
此说甚善。能发朱子所未发之意。然必以此一节为起下文。而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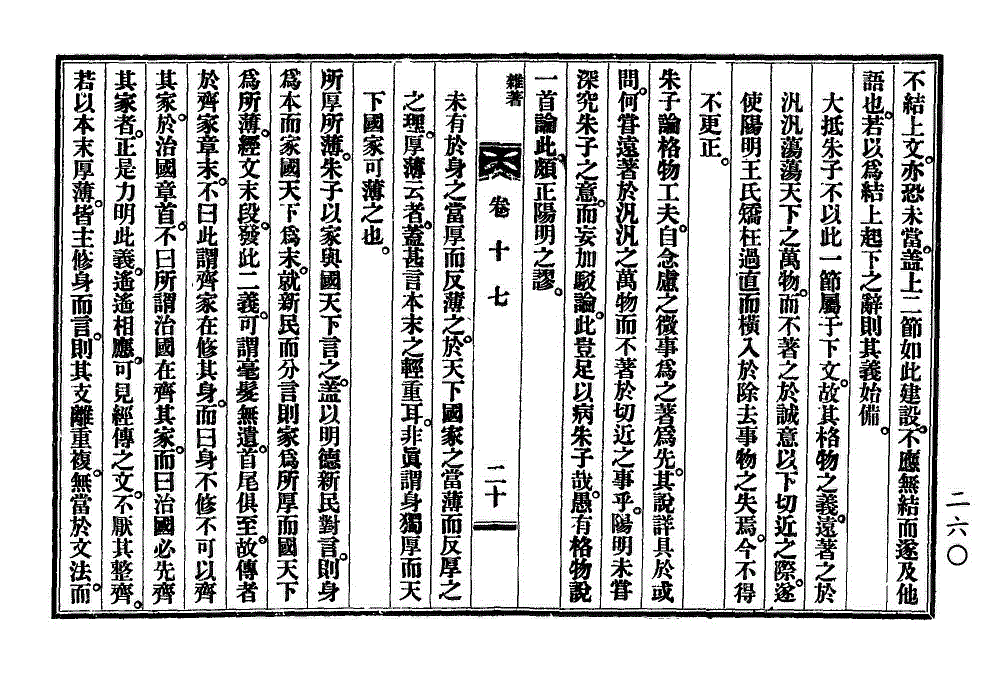 不结上文。亦恐未当。盖上二节如此建设。不应无结而遂及他语也。若以为结上起下之辞则其义始备。
不结上文。亦恐未当。盖上二节如此建设。不应无结而遂及他语也。若以为结上起下之辞则其义始备。大抵朱子不以此一节属于下文。故其格物之义。远著之于汎汎荡荡天下之万物。而不著之于诚意以下切近之际。遂使阳明王氏矫枉过直而横入于除去事物之失焉。今不得不更正。
朱子论格物工夫。自念虑之微事为之著为先。其说详具于或问。何尝远著于汎汎之万物而不著于切近之事乎。阳明未尝深究朱子之意。而妄加驳论。此岂足以病朱子哉。愚有格物说一首论此。颇正阳明之谬。
未有于身之当厚而反薄之。于天下国家之当薄而反厚之之理。厚薄云者。盖甚言本末之轻重耳。非真谓身独厚而天下国家可薄之也。
所厚所薄。朱子以家与国天下言之。盖以明德新民对言。则身为本而家国天下为末。就新民而分言则家为所厚而国天下为所薄。经文末段。发此二义。可谓毫发无遗。首尾俱至。故传者于齐家章末。不曰此谓齐家在修其身。而曰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于治国章首。不曰所谓治国在齐其家。而曰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正是力明此义。遥遥相应。可见经传之文。不厌其整齐。若以本末厚薄。皆主修身而言。则其支离重复。无当于文法。而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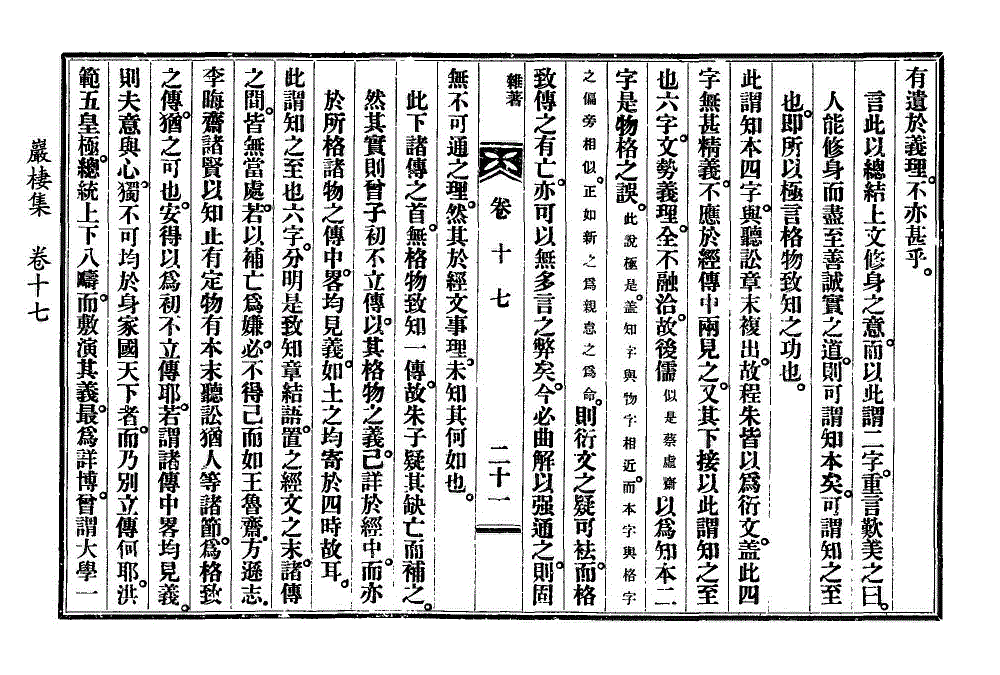 有遗于义理。不亦甚乎。
有遗于义理。不亦甚乎。言此以总结上文修身之意。而以此谓二字。重言叹美之曰。人能修身而尽至善诚实之道。则可谓知本矣。可谓知之至也。即所以极言格物致知之功也。
此谓知本四字。与听讼章末复出。故程朱皆以为衍文。盖此四字无甚精义。不应于经传中两见之。又其下接以此谓知之至也六字。文势义理。全不融洽。故后儒(似是蔡虚斋)以为知本二字是物格之误。(此说极是。盖知字与物字相近。而本字与格字之偏旁相似。正如新之为亲怠之为命。)则衍文之疑可袪。而格致传之有亡。亦可以无多言之弊矣。今必曲解以强通之。则固无不可通之理。然其于经文事理。未知其何如也。
此下诸传之首。无格物致知一传。故朱子疑其缺亡而补之。然其实则曾子初不立传。以其格物之义。已详于经中。而亦于所格诸物之传中。略均见义。如土之均寄于四时故耳。
此谓知之至也六字。分明是致知章结语。置之经文之末。诸传之间。皆无当处。若以补亡为嫌。必不得已而如王鲁斋,方逊志,李晦斋诸贤以知止有定物有本末听讼犹人等诸节。为格致之传。犹之可也。安得以为初不立传耶。若谓诸传中略均见义。则夫意与心。独不可均于身家国天下者。而乃别立传何耶。洪范五皇极。总统上下八畴。而敷演其义。最为详博。曾谓大学一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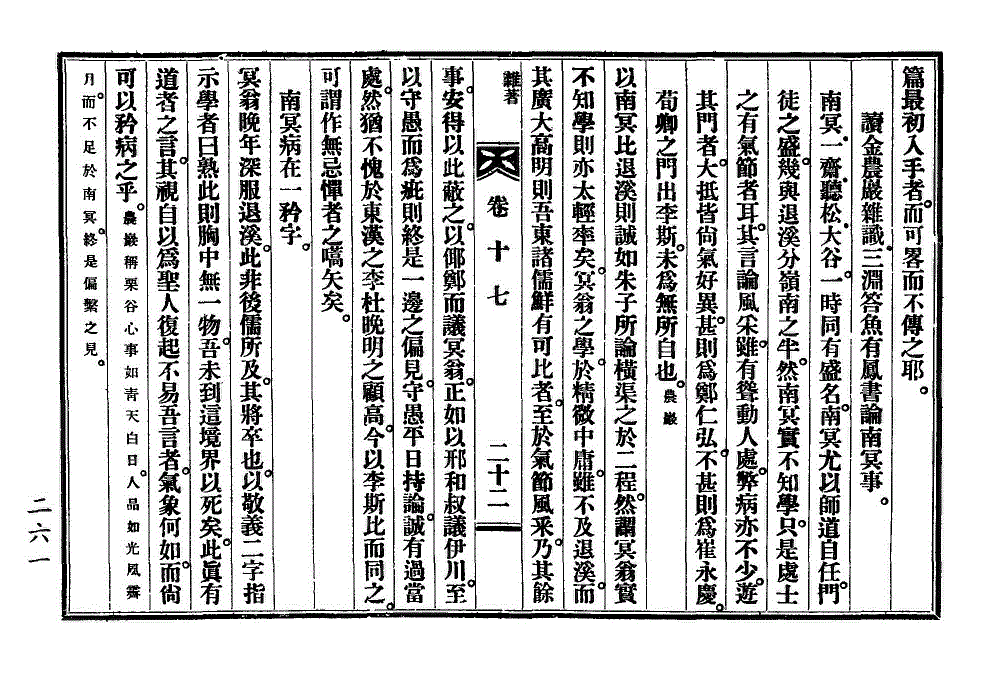 篇最初入手者。而可略而不传之耶。
篇最初入手者。而可略而不传之耶。读金农岩杂识,三渊答鱼有凤书论南冥事。
南冥,一斋,听松,大谷。一时同有盛名。南冥尤以师道自任。门徒之盛。几与退溪分岭南之半。然南冥实不知学。只是处士之有气节者耳。其言论风采。虽有耸动人处。弊病亦不少。游其门者。大抵皆尚气好异。甚则为郑仁弘。不甚则为崔永庆。荀卿之门出李斯。未为无所自也。(农岩)
以南冥比退溪则诚如朱子所论横渠之于二程。然谓冥翁实不知学则亦太轻率矣。冥翁之学。于精微中庸。虽不及退溪。而其广大高明则吾东诸儒鲜有可比者。至于气节风采。乃其馀事。安得以此蔽之。以倻郑而议冥翁。正如以邢和叔议伊川。至以守愚而为疵则终是一边之偏见。守愚平日持论。诚有过当处。然犹不愧于东汉之李杜晚明之顾高。今以李斯比而同之。可谓作无忌惮者之嚆矢矣。
南冥病在一矜字。
冥翁晚年深服退溪。此非后儒所及。其将卒也。以敬义二字指示学者曰熟此则胸中无一物。吾未到这境界以死矣。此真有道者之言。其视自以为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者。气象何如。而尚可以矜病之乎。(农岩称栗谷心事如青天白日。人品如光风霁月。而不足于南冥。终是偏系之见。)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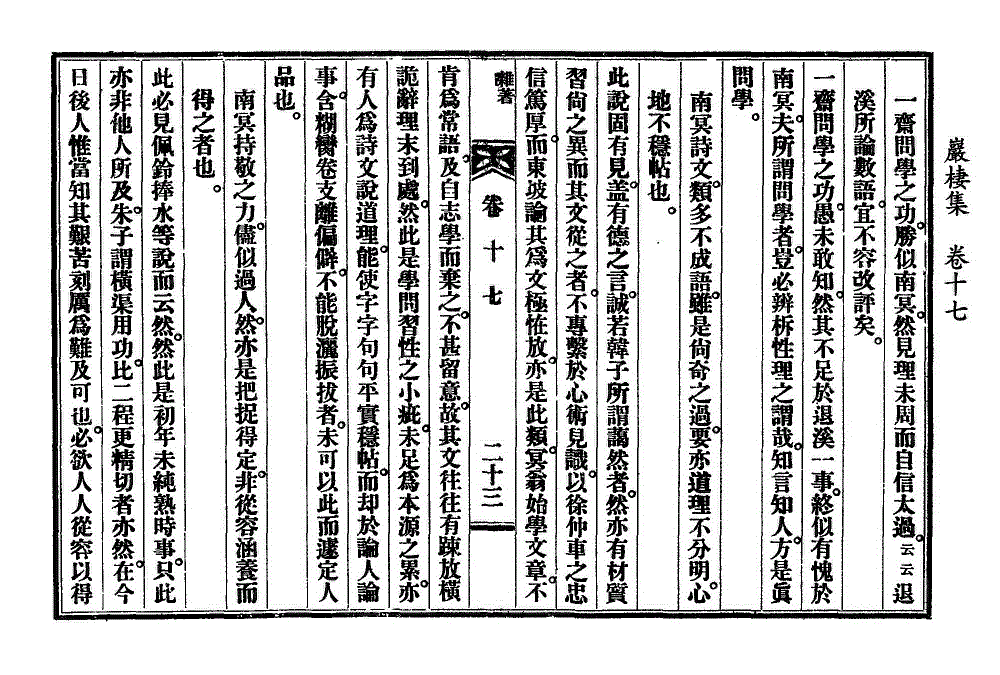 一斋问学之功。胜似南冥。然见理未周而自信太过。(云云)退溪所论数语。宜不容改评矣。
一斋问学之功。胜似南冥。然见理未周而自信太过。(云云)退溪所论数语。宜不容改评矣。一斋问学之功。愚未敢知。然其不足于退溪一事。终似有愧于南冥。夫所谓问学者。岂必辨柝性理之谓哉。知言知人。方是真问学。
南冥诗文。类多不成语。虽是尚奇之过。要亦道理不分明。心地不稳帖也。
此说固有见。盖有德之言。诚若韩子所谓蔼然者。然亦有材质习尚之异而其文从之者。不专系于心术见识。以徐仲车之忠信笃厚。而东坡论其为文极怪放。亦是此类。冥翁始学文章。不肯为常语。及自志学而弃之。不甚留意。故其文往往有疏放横诡辞理末到处。然此是学问习性之小疵。未足为本源之累。亦有人为诗文说道理。能使字字句句平实稳帖。而却于论人论事。含糊脔卷支离偏僻。不能脱洒振拔者。未可以此而遽定人品也。
南冥持敬之力。尽似过人。然亦是把捉得定。非从容涵养而得之者也。
此必见佩铃捧水等说而云然。然此是初年未纯熟时事。只此亦非他人所及。朱子谓横渠用功。比二程更精切者亦然。在今日后人惟当知其艰苦刻厉为难及可也。必欲人人从容以得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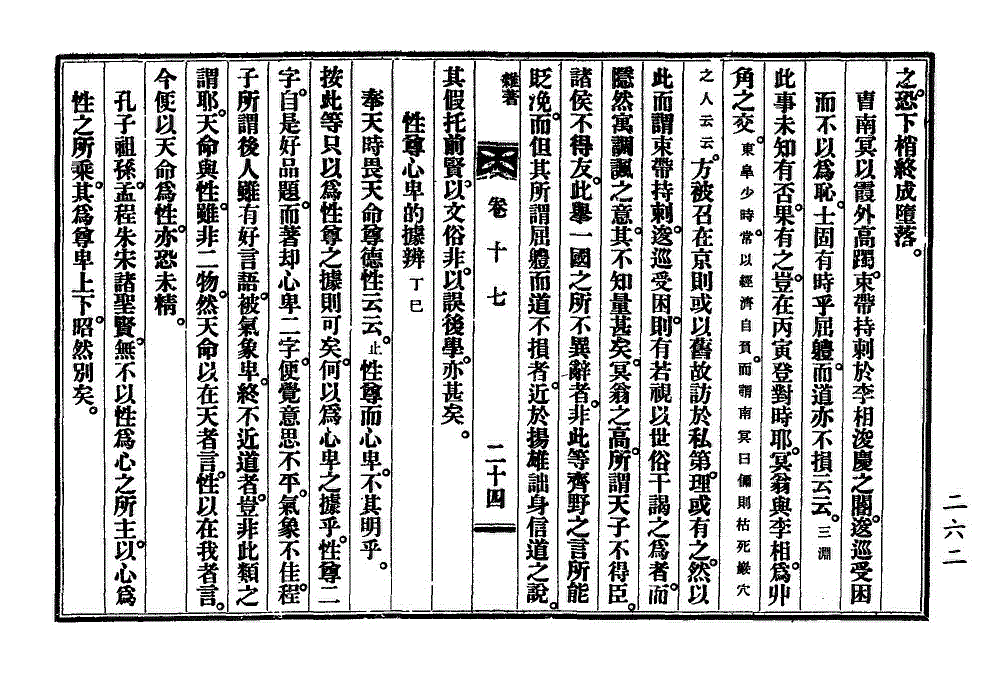 之。恐下梢终成堕落。
之。恐下梢终成堕落。曹南冥以霞外高躅。束带持刺于李相浚庆之阍。逡巡受困而不以为耻。士固有时乎屈体。而道亦不损云云。(三渊)
此事未知有否。果有之。岂在丙寅登对时耶。冥翁与李相。为丱角之交。(东皋少时。常以经济自负。而谓南冥曰你则枯死岩穴之人云云。)方被召在京则或以旧故访于私第。理或有之。然以此而谓束带持刺。逡巡受困。则有若视以世俗干谒之为者。而隐然寓调讽之意。其不知量甚矣。冥翁之高。所谓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此举一国之所不异辞者。非此等齐野之言所能贬浼。而但其所谓屈体而道不损者。近于扬雄诎身信道之说。其假托前贤。以文俗非。以误后学。亦甚矣。
性尊心卑的据辨(丁巳)
奉天时畏天命尊德性云云。(止)性尊而心卑。不其明乎。
按此等只以为性尊之据则可矣。何以为心卑之据乎。性尊二字。自是好品题。而著却心卑二字。便觉意思不平。气象不佳。程子所谓后人虽有好言语。被气象卑。终不近道者。岂非此类之谓耶。天命与性。虽非二物。然天命以在天者言。性以在我者言。今便以天命为性。亦恐未精。
孔子祖孙。孟程朱宋诸圣贤。无不以性为心之所主。以心为性之所乘。其为尊卑上下。昭然别矣。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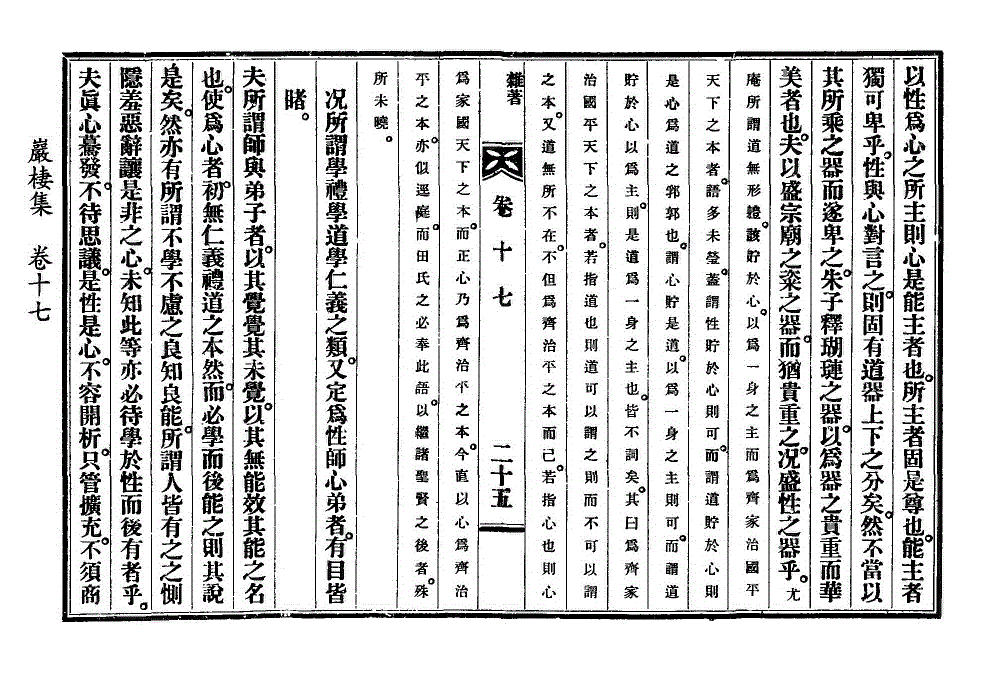 以性为心之所主则心是能主者也。所主者固是尊也。能主者独可卑乎。性与心对言之。则固有道器上下之分矣。然不当以其所乘之器而遂卑之。朱子释瑚琏之器。以为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夫以盛宗庙之粢之器。而犹贵重之。况盛性之器乎。(尤庵所谓道无形体。该贮于心。以为一身之主而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语多未莹。盖谓性贮于心则可。而谓道贮于心则是心为道之郛郭也。谓心贮是道。以为一身之主则可。而谓道贮于心以为主。则是道为一身之主也。皆不词矣。其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若指道也则道可以谓之则而不可以谓之本。又道无所不在。不但为齐治平之本而已。若指心也则心为家国天下之本。而正心乃为齐治平之本。今直以心为齐治平之本。亦似径庭。而田氏之必奉此语。以继诸圣贤之后者。殊所未晓。)
以性为心之所主则心是能主者也。所主者固是尊也。能主者独可卑乎。性与心对言之。则固有道器上下之分矣。然不当以其所乘之器而遂卑之。朱子释瑚琏之器。以为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夫以盛宗庙之粢之器。而犹贵重之。况盛性之器乎。(尤庵所谓道无形体。该贮于心。以为一身之主而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语多未莹。盖谓性贮于心则可。而谓道贮于心则是心为道之郛郭也。谓心贮是道。以为一身之主则可。而谓道贮于心以为主。则是道为一身之主也。皆不词矣。其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若指道也则道可以谓之则而不可以谓之本。又道无所不在。不但为齐治平之本而已。若指心也则心为家国天下之本。而正心乃为齐治平之本。今直以心为齐治平之本。亦似径庭。而田氏之必奉此语。以继诸圣贤之后者。殊所未晓。)况所谓学礼学道学仁义之类。又定为性师心弟者。有目皆睹。
夫所谓师与弟子者。以其觉觉其未觉。以其无能效其能之名也。使为心者。初无仁义礼道之本然。而必学而后能之则其说是矣。然亦有所谓不学不虑之良知良能。所谓人皆有之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未知此等亦必待学于性而后有者乎。夫真心蓦发。不待思议。是性是心。不容开析。只管扩充。不须商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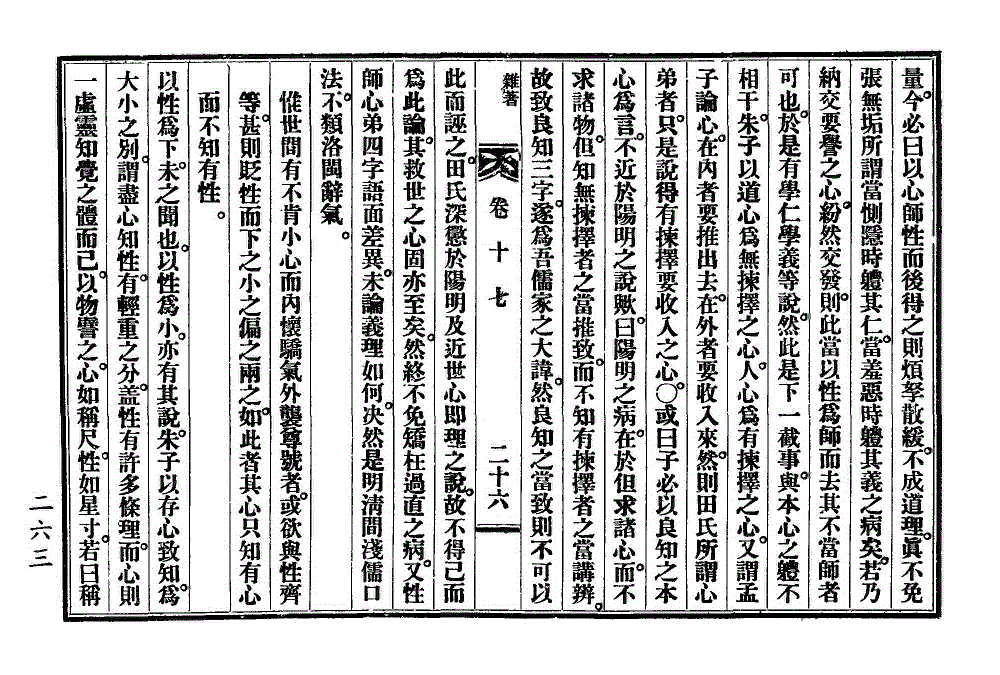 量。今必曰以心师性而后得之则烦孥散缓。不成道理。真不免张无垢所谓当恻隐时体其仁。当羞恶时体其义之病矣。若乃纳交要誉之心。纷然交发。则此当以性为师而去其不当师者可也。于是有学仁学义等说。然此是下一截事。与本心之体不相干。朱子以道心为无拣择之心。人心为有拣择之心。又谓孟子论心。在内者要推出去。在外者要收入来。然则田氏所谓心弟者。只是说得有拣择要收入之心。○或曰子必以良知之本心为言。不近于阳明之说欤。曰阳明之病。在于但求诸心。而不求诸物。但知无拣择者之当推致。而不知有拣择者之当讲辨。故致良知三字。遂为吾儒家之大讳。然良知之当致则不可以此而诬之。田氏深惩于阳明及近世心即理之说。故不得已而为此论。其救世之心固亦至矣。然终不免矫枉过直之病。又性师心弟四字语面差异。未论义理如何。决然是明清间浅儒口法。不类洛闽辞气。
量。今必曰以心师性而后得之则烦孥散缓。不成道理。真不免张无垢所谓当恻隐时体其仁。当羞恶时体其义之病矣。若乃纳交要誉之心。纷然交发。则此当以性为师而去其不当师者可也。于是有学仁学义等说。然此是下一截事。与本心之体不相干。朱子以道心为无拣择之心。人心为有拣择之心。又谓孟子论心。在内者要推出去。在外者要收入来。然则田氏所谓心弟者。只是说得有拣择要收入之心。○或曰子必以良知之本心为言。不近于阳明之说欤。曰阳明之病。在于但求诸心。而不求诸物。但知无拣择者之当推致。而不知有拣择者之当讲辨。故致良知三字。遂为吾儒家之大讳。然良知之当致则不可以此而诬之。田氏深惩于阳明及近世心即理之说。故不得已而为此论。其救世之心固亦至矣。然终不免矫枉过直之病。又性师心弟四字语面差异。未论义理如何。决然是明清间浅儒口法。不类洛闽辞气。惟世间有不肯小心而内怀骄气外袭尊号者。或欲与性齐等。甚则贬性而下之小之偏之两之。如此者其心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
以性为下。未之闻也。以性为小。亦有其说。朱子以存心致知。为大小之别。谓尽心知性。有轻重之分。盖性有许多条理。而心则一虚灵知觉之体而已。以物譬之。心如称尺。性如星寸。若曰称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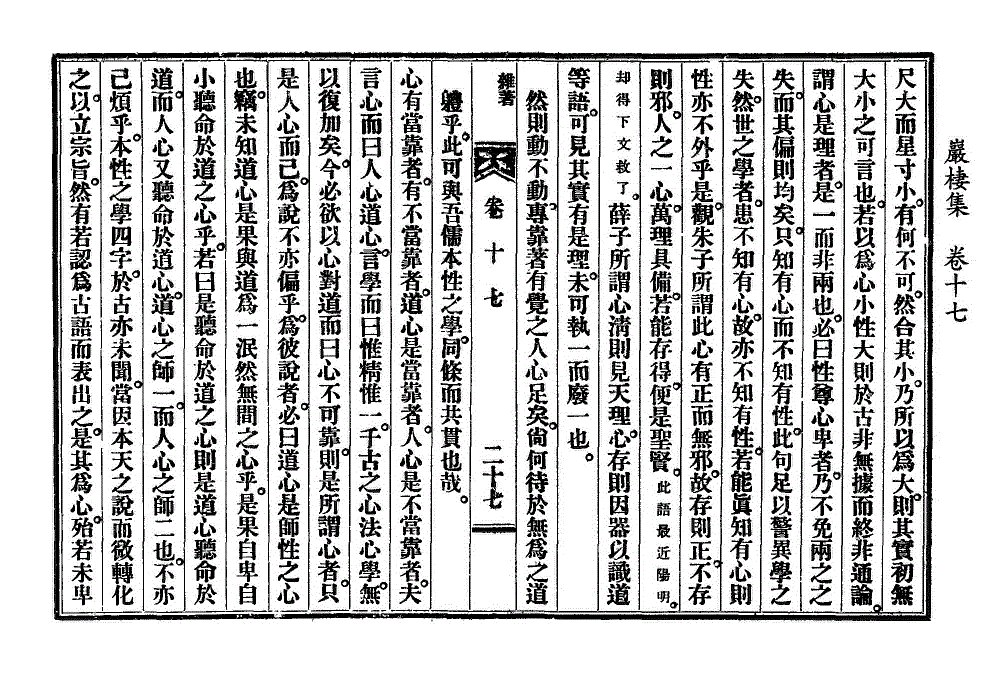 尺大而星寸小。有何不可。然合其小。乃所以为大。则其实初无大小之可言也。若以为心小性大则于古非无据而终非通论。谓心是理者。是一而非两也。必曰性尊心卑者。乃不免两之之失。而其偏则均矣。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此句足以警异学之失。然世之学者。患不知有心。故亦不知有性。若能真知有心则性亦不外乎是。观朱子所谓此心有正而无邪。故存则正。不存则邪。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此语最近阳明。却得下文救了。)薜子所谓心清则见天理。心存则因器以识道等语。可见其实有是理。未可执一而废一也。
尺大而星寸小。有何不可。然合其小。乃所以为大。则其实初无大小之可言也。若以为心小性大则于古非无据而终非通论。谓心是理者。是一而非两也。必曰性尊心卑者。乃不免两之之失。而其偏则均矣。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此句足以警异学之失。然世之学者。患不知有心。故亦不知有性。若能真知有心则性亦不外乎是。观朱子所谓此心有正而无邪。故存则正。不存则邪。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此语最近阳明。却得下文救了。)薜子所谓心清则见天理。心存则因器以识道等语。可见其实有是理。未可执一而废一也。然则动不动。专靠著有觉之人心足矣。尚何待于无为之道体乎。此可与吾儒本性之学。同条而共贯也哉。
心有当靠者。有不当靠者。道心是当靠者。人心是不当靠者。夫言心而曰人心道心。言学而曰惟精惟一。千古之心法心学。无以复加矣。今必欲以心对道而曰心不可靠。则是所谓心者。只是人心而已。为说不亦偏乎。为彼说者。必曰道心是师性之心也。窃未知道心是果与道为一泯然无间之心乎。是果自卑自小听命于道之心乎。若曰是听命于道之心则是道心听命于道。而人心又听命于道心。道心之师一。而人心之师二也。不亦已烦乎。本性之学四字。于古亦未闻。当因本天之说而微转化之。以立宗旨。然有若认为古语而表出之。是其为心。殆若未卑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4L 页
 然。(闻田氏所居学者之室。有海东千载性师翁之标榜。此与瞿昙氏惟我独尊者。同一意概。而乃力攻本心之学。不近于履其实而辞其名者耶。且其以奉天时之大人。尊德性之君子。皆为包心言。以此例之。翁亦当包心。而其尊之若此。则心之不卑。又可知矣。)
然。(闻田氏所居学者之室。有海东千载性师翁之标榜。此与瞿昙氏惟我独尊者。同一意概。而乃力攻本心之学。不近于履其实而辞其名者耶。且其以奉天时之大人。尊德性之君子。皆为包心言。以此例之。翁亦当包心。而其尊之若此。则心之不卑。又可知矣。)张子曰心统性情。朱子曰心为性情之主宰。此类但以人心有觉。道体无为而云尔。非所以为上下尊卑之别也。或以是为心尊性卑之说则谬矣。朱子尝言天子统摄天地。又言人者天地之心。没这人时。天地便无人管。此以天地无思虑无句当。圣贤尽人物赞化育而言。岂可以此为人心尊于天地乎。
心统性情。心为性情之主宰。(朱子又有心者性情之主一句。今舍而不举何耶。)二语若出于今人之口。则窃恐田氏必且大言其谬矣。惟其为先儒大贤之言。故不得不曲为證解。然凡言有立言之言。有推说之言。张朱二言。是立言之言也。故平常切当。虽孤行此句。更不可移易。至下所引朱子二说则是推说之言也。若以此而立言曰天子统天地者也。(心统性情下。本有者也二字。)人者天地之主云尔。则亦可以为平常切当不可移易之训乎。窃尝譬之。心统性情。犹言君统民社。心者性情之主。犹言君者神人之主。夫君为民社而设。故君必念念在民社。然后方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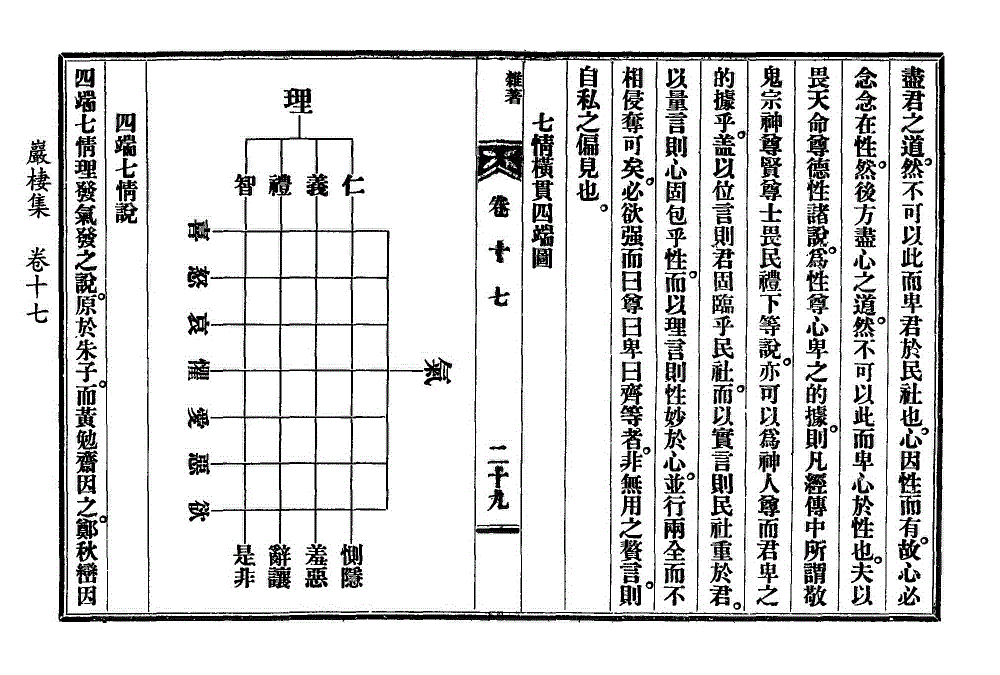 尽君之道。然不可以此而卑君于民社也。心因性而有。故心必念念在性。然后方尽心之道。然不可以此而卑心于性也。夫以畏天命尊德性诸说。为性尊心卑之的据。则凡经传中所谓敬鬼宗神尊贤尊士畏民礼下等说。亦可以为神人尊而君卑之的据乎。盖以位言则君固临乎民社。而以实言则民社重于君。以量言则心固包乎性。而以理言则性妙于心。并行两全而不相侵夺可矣。必欲强而曰尊曰卑曰齐等者。非无用之赘言。则自私之偏见也。
尽君之道。然不可以此而卑君于民社也。心因性而有。故心必念念在性。然后方尽心之道。然不可以此而卑心于性也。夫以畏天命尊德性诸说。为性尊心卑之的据。则凡经传中所谓敬鬼宗神尊贤尊士畏民礼下等说。亦可以为神人尊而君卑之的据乎。盖以位言则君固临乎民社。而以实言则民社重于君。以量言则心固包乎性。而以理言则性妙于心。并行两全而不相侵夺可矣。必欲强而曰尊曰卑曰齐等者。非无用之赘言。则自私之偏见也。七情横贯四端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四端七情说
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说。原于朱子。而黄勉斋因之。郑秋峦因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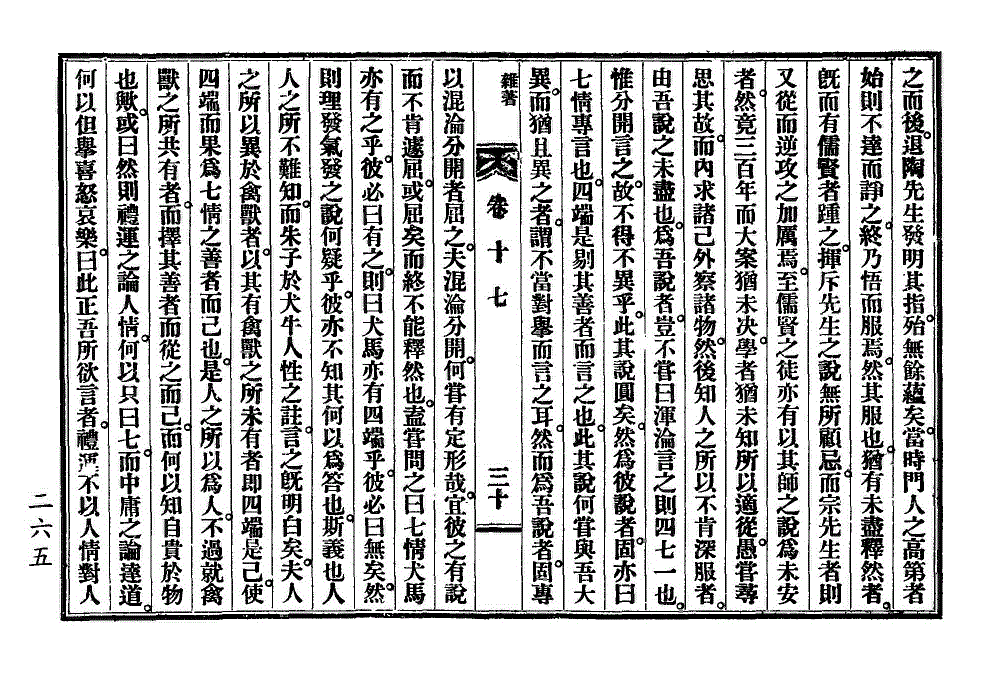 之而后。退陶先生发明其指。殆无馀蕴矣。当时门人之高第者始则不达而诤之。终乃悟而服焉。然其服也。犹有未尽释然者。既而有儒贤者踵之。挥斥先生之说无所顾忌。而宗先生者则又从而逆攻之加厉焉。至儒贤之徒亦有以其师之说为未安者。然竟三百年而大案犹未决。学者犹未知所以适从。愚尝寻思其故。而内求诸己外察诸物。然后知人之所以不肯深服者。由吾说之未尽也。为吾说者。岂不尝曰浑沦言之则四七一也。惟分开言之。故不得不异乎。此其说圆矣。然为彼说者。固亦曰七情专言也。四端是剔其善者而言之也。此其说何尝与吾大异。而犹且异之者。谓不当对举而言之耳。然而为吾说者。固专以混沦分开者屈之。夫混沦分开。何尝有定形哉。宜彼之有说而不肯遽屈。或屈矣而终不能释然也。盍尝问之曰七情犬马亦有之乎。彼必曰有之。则曰犬马亦有四端乎。彼必曰无矣。然则理发气发之说何疑乎。彼亦不知其何以为答也。斯义也人人之所不难知。而朱子于犬牛人性之注。言之既明白矣。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禽兽之所未有者即四端是已。使四端而果为七情之善者而已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不过就禽兽之所共有者。而择其善者而从之而已。而何以知自贵于物也欤。或曰然则礼运之论人情。何以只曰七。而中庸之论达道。何以但举喜怒哀乐。曰此正吾所欲言者。礼运不以人情对人
之而后。退陶先生发明其指。殆无馀蕴矣。当时门人之高第者始则不达而诤之。终乃悟而服焉。然其服也。犹有未尽释然者。既而有儒贤者踵之。挥斥先生之说无所顾忌。而宗先生者则又从而逆攻之加厉焉。至儒贤之徒亦有以其师之说为未安者。然竟三百年而大案犹未决。学者犹未知所以适从。愚尝寻思其故。而内求诸己外察诸物。然后知人之所以不肯深服者。由吾说之未尽也。为吾说者。岂不尝曰浑沦言之则四七一也。惟分开言之。故不得不异乎。此其说圆矣。然为彼说者。固亦曰七情专言也。四端是剔其善者而言之也。此其说何尝与吾大异。而犹且异之者。谓不当对举而言之耳。然而为吾说者。固专以混沦分开者屈之。夫混沦分开。何尝有定形哉。宜彼之有说而不肯遽屈。或屈矣而终不能释然也。盍尝问之曰七情犬马亦有之乎。彼必曰有之。则曰犬马亦有四端乎。彼必曰无矣。然则理发气发之说何疑乎。彼亦不知其何以为答也。斯义也人人之所不难知。而朱子于犬牛人性之注。言之既明白矣。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禽兽之所未有者即四端是已。使四端而果为七情之善者而已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不过就禽兽之所共有者。而择其善者而从之而已。而何以知自贵于物也欤。或曰然则礼运之论人情。何以只曰七。而中庸之论达道。何以但举喜怒哀乐。曰此正吾所欲言者。礼运不以人情对人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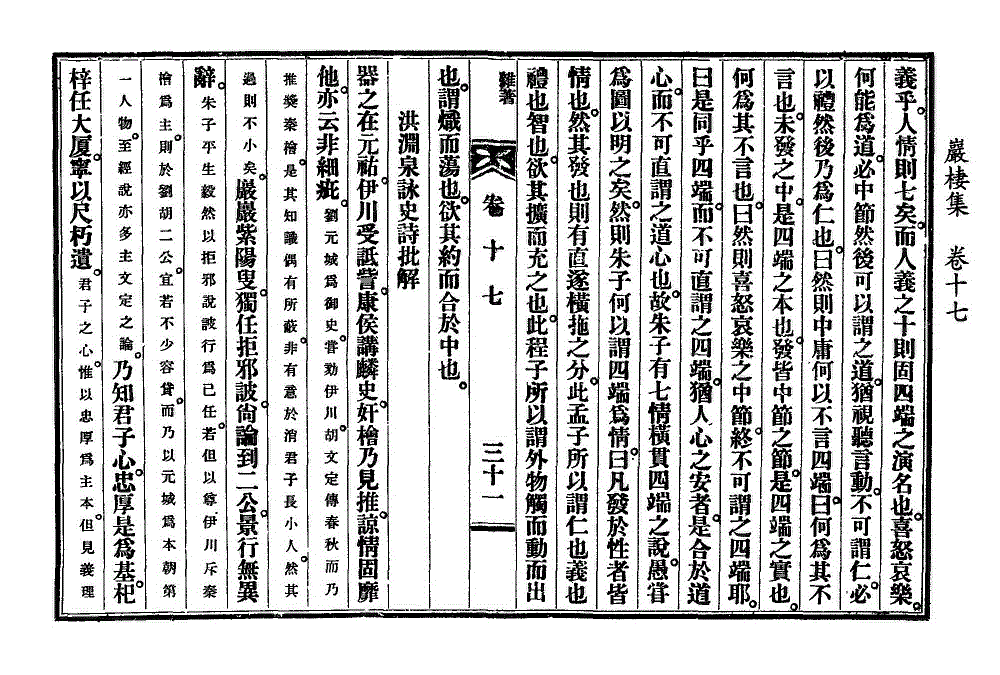 义乎。人情则七矣。而人义之十则固四端之演名也。喜怒哀乐。何能为道。必中节然后可以谓之道。犹视听言动。不可谓仁。必以礼然后乃为仁也。曰然则中庸何以不言四端。曰何为其不言也。未发之中。是四端之本也。发皆中节之节。是四端之实也。何为其不言也。曰然则喜怒哀乐之中节。终不可谓之四端耶。曰是同乎四端。而不可直谓之四端。犹人心之安者。是合于道心。而不可直谓之道心也。故朱子有七情横贯四端之说。愚尝为图以明之矣。然则朱子何以谓四端为情。曰凡发于性者皆情也。然其发也则有直遂横拖之分。此孟子所以谓仁也义也礼也智也。欲其扩而充之也。此程子所以谓外物触而动而出也。谓炽而荡也。欲其约而合于中也。
义乎。人情则七矣。而人义之十则固四端之演名也。喜怒哀乐。何能为道。必中节然后可以谓之道。犹视听言动。不可谓仁。必以礼然后乃为仁也。曰然则中庸何以不言四端。曰何为其不言也。未发之中。是四端之本也。发皆中节之节。是四端之实也。何为其不言也。曰然则喜怒哀乐之中节。终不可谓之四端耶。曰是同乎四端。而不可直谓之四端。犹人心之安者。是合于道心。而不可直谓之道心也。故朱子有七情横贯四端之说。愚尝为图以明之矣。然则朱子何以谓四端为情。曰凡发于性者皆情也。然其发也则有直遂横拖之分。此孟子所以谓仁也义也礼也智也。欲其扩而充之也。此程子所以谓外物触而动而出也。谓炽而荡也。欲其约而合于中也。洪渊泉咏史诗批解
器之在元祐。伊川受诋訾。康侯讲麟史。奸桧乃见推。谅情固靡他。亦云非细疵。(刘元城为御史。尝劾伊川。胡文定传春秋而乃推奖秦桧。是其知识偶有所蔽。非有意于消君子长小人。然其过则不小矣。)岩岩紫阳叟。独任拒邪诐。尚论到二公。景行无异辞。(朱子平生毅然以拒邪说诐行为己任。若但以尊伊川斥秦桧为主。则于刘胡二公。宜若不少容贷。而乃以元城为本朝第一人物。至经说亦多主文定之论。)乃知君子心。忠厚是为基。杞梓任大厦。宁以尺朽遗。(君子之心。惟以忠厚为主本。但见义理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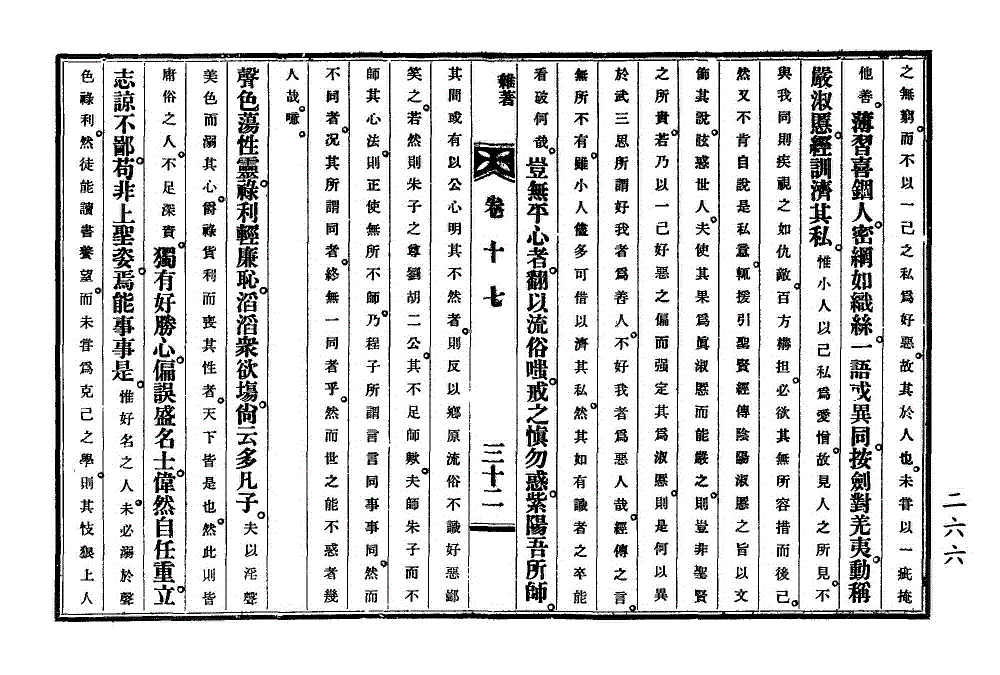 之无穷。而不以一己之私为好恶。故其于人也。未尝以一疵掩他善。)薄习喜锢人。密网如织丝。一语或异同。按剑对羌夷。动称严淑慝。经训济其私。(惟小人以己私为爱憎。故见人之所见。不与我同则疾视之如仇敌。百方构担。必欲其无所容措而后已。然又不肯自说是私意。辄援引圣贤经传阴阳淑慝之旨以文饰其说。眩惑世人。夫使其果为真淑慝而能严之。则岂非圣贤之所贵。若乃以一己好恶之偏而强定其为淑慝。则是何以异于武三思所谓好我者为善人。不好我者为恶人哉。经传之言。无所不有。虽小人尽多可借以济其私。然其如有识者之卒能看破何哉。)岂无平心者。翻以流俗嗤。戒之慎勿惑。紫阳吾所师。(其间或有以公心明其不然者。则反以乡原流俗不识好恶鄙笑之。若然则朱子之尊刘胡二公。其不足师欤。夫师朱子而不师其心法。则正使无所不师。乃程子所谓言言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者。况其所谓同者。终无一同者乎。然而世之能不惑者几人哉。噫。)
之无穷。而不以一己之私为好恶。故其于人也。未尝以一疵掩他善。)薄习喜锢人。密网如织丝。一语或异同。按剑对羌夷。动称严淑慝。经训济其私。(惟小人以己私为爱憎。故见人之所见。不与我同则疾视之如仇敌。百方构担。必欲其无所容措而后已。然又不肯自说是私意。辄援引圣贤经传阴阳淑慝之旨以文饰其说。眩惑世人。夫使其果为真淑慝而能严之。则岂非圣贤之所贵。若乃以一己好恶之偏而强定其为淑慝。则是何以异于武三思所谓好我者为善人。不好我者为恶人哉。经传之言。无所不有。虽小人尽多可借以济其私。然其如有识者之卒能看破何哉。)岂无平心者。翻以流俗嗤。戒之慎勿惑。紫阳吾所师。(其间或有以公心明其不然者。则反以乡原流俗不识好恶鄙笑之。若然则朱子之尊刘胡二公。其不足师欤。夫师朱子而不师其心法。则正使无所不师。乃程子所谓言言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者。况其所谓同者。终无一同者乎。然而世之能不惑者几人哉。噫。)声色荡性灵。禄利轻廉耻。滔滔众欲场。尚云多凡子。(夫以淫声美色而溺其心。爵禄货利而丧其性者。天下皆是也。然此则皆庸俗之人。不足深责。)独有好胜心。偏误盛名士。伟然自任重。立志谅不鄙。苟非上圣姿。焉能事事是。(惟好名之人。未必溺于声色禄利。然徒能读书养望。而未尝为克己之学。则其忮狠上人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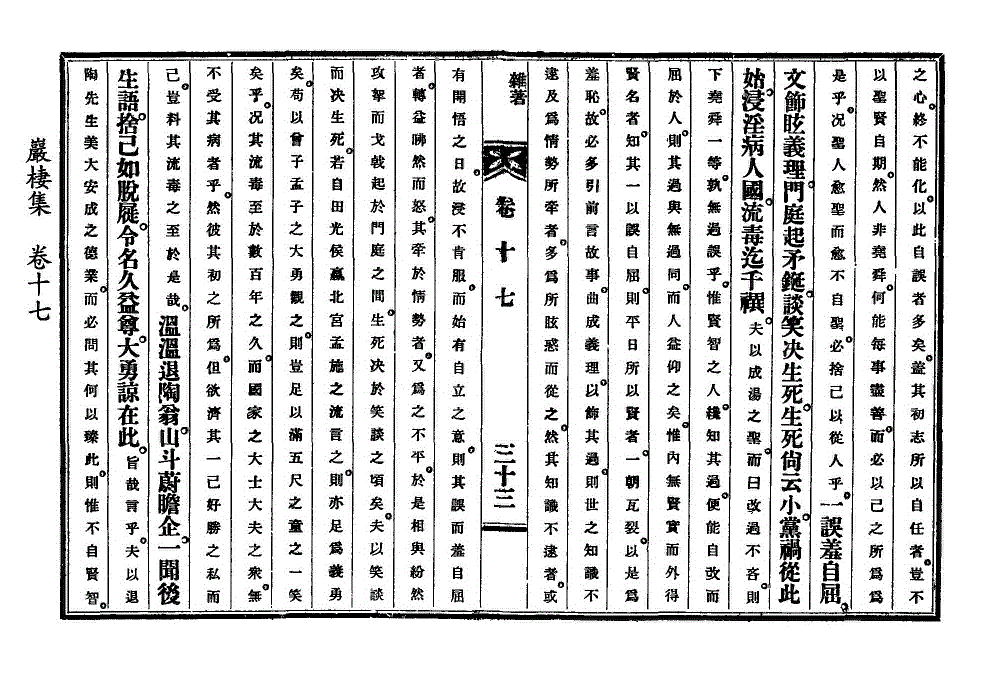 之心。终不能化。以此自误者多矣。盖其初志所以自任者。岂不以圣贤自期。然人非尧舜。何能每事尽善。而必以己之所为为是乎。况圣人愈圣而愈不自圣。必舍己以从人乎。)一误羞自屈。文饰眩义理。门庭起矛鋋。谈笑决生死。生死尚云小。党祸从此始。浸淫病人国。流毒迄千祀。(夫以成汤之圣。而曰改过不吝。则下尧舜一等。孰无过误乎。惟贤智之人。才知其过。便能自改而屈于人。则其过与无过同。而人益仰之矣。惟内无贤实而外得贤名者。知其一以误自屈。则平日所以贤者。一朝瓦裂。以是为羞耻。故必多引前言故事。曲成义理。以饰其过。则世之知识不逮及为情势所牵者。多为所眩惑而从之。然其知识不逮者。或有开悟之日。故浸不肯服。而始有自立之意。则其误而羞自屈者。转益咈然而怒。其牵于情势者。又为之不平。于是相与纷然攻挐而戈戟起于门庭之间。生死决于笑谈之顷矣。夫以笑谈而决生死。若自田光侯嬴北宫孟施之流言之。则亦足为义勇矣。苟以曾子孟子之大勇观之。则岂足以满五尺之童之一笑矣乎。况其流毒至于数百年之久。而国家之大士大夫之众。无不受其病者乎。然彼其初之所为。但欲济其一己好胜之私而已。岂料其流毒之至于是哉。)温温退陶翁。山斗蔚瞻企。一闻后生语。舍己如脱屣。令名久益尊。大勇谅在此。(旨哉言乎。未以退陶先生美大安成之德业。而必问其何以臻此。则惟不自贤智。
之心。终不能化。以此自误者多矣。盖其初志所以自任者。岂不以圣贤自期。然人非尧舜。何能每事尽善。而必以己之所为为是乎。况圣人愈圣而愈不自圣。必舍己以从人乎。)一误羞自屈。文饰眩义理。门庭起矛鋋。谈笑决生死。生死尚云小。党祸从此始。浸淫病人国。流毒迄千祀。(夫以成汤之圣。而曰改过不吝。则下尧舜一等。孰无过误乎。惟贤智之人。才知其过。便能自改而屈于人。则其过与无过同。而人益仰之矣。惟内无贤实而外得贤名者。知其一以误自屈。则平日所以贤者。一朝瓦裂。以是为羞耻。故必多引前言故事。曲成义理。以饰其过。则世之知识不逮及为情势所牵者。多为所眩惑而从之。然其知识不逮者。或有开悟之日。故浸不肯服。而始有自立之意。则其误而羞自屈者。转益咈然而怒。其牵于情势者。又为之不平。于是相与纷然攻挐而戈戟起于门庭之间。生死决于笑谈之顷矣。夫以笑谈而决生死。若自田光侯嬴北宫孟施之流言之。则亦足为义勇矣。苟以曾子孟子之大勇观之。则岂足以满五尺之童之一笑矣乎。况其流毒至于数百年之久。而国家之大士大夫之众。无不受其病者乎。然彼其初之所为。但欲济其一己好胜之私而已。岂料其流毒之至于是哉。)温温退陶翁。山斗蔚瞻企。一闻后生语。舍己如脱屣。令名久益尊。大勇谅在此。(旨哉言乎。未以退陶先生美大安成之德业。而必问其何以臻此。则惟不自贤智。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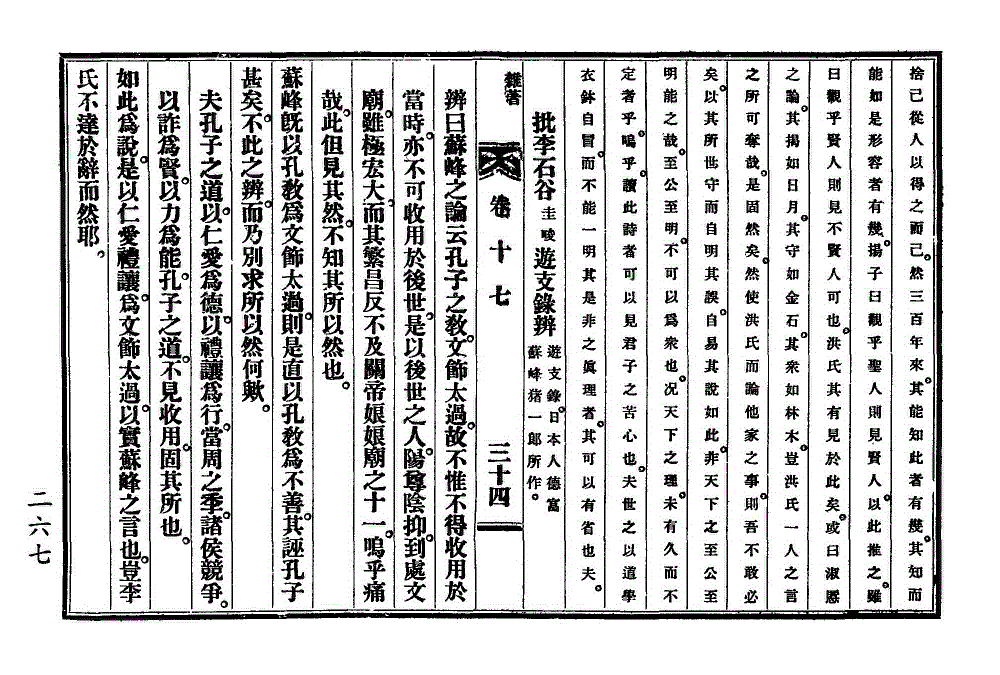 舍己从人以得之而已。然三百年来。其能知此者有几。其知而能如是形容者有几。扬子曰观乎圣人则见贤人。以此推之。虽曰观乎贤人则见不贤人可也。洪氏其有见于此矣。或曰淑慝之论。其揭如日月。其守如金石。其众如林木。岂洪氏一人之言之所可夺哉。是固然矣。然使洪氏而论他家之事。则吾不敢必矣。以其所世守而自明其误。自易其说如此。非天下之至公至明能之哉。至公至明。不可以为众也。况天下之理。未有久而不定者乎。呜乎。读此诗者可以见君子之苦心也。夫世之以道学衣钵自冒。而不能一明其是非之真理者。其可以有省也夫。)
舍己从人以得之而已。然三百年来。其能知此者有几。其知而能如是形容者有几。扬子曰观乎圣人则见贤人。以此推之。虽曰观乎贤人则见不贤人可也。洪氏其有见于此矣。或曰淑慝之论。其揭如日月。其守如金石。其众如林木。岂洪氏一人之言之所可夺哉。是固然矣。然使洪氏而论他家之事。则吾不敢必矣。以其所世守而自明其误。自易其说如此。非天下之至公至明能之哉。至公至明。不可以为众也。况天下之理。未有久而不定者乎。呜乎。读此诗者可以见君子之苦心也。夫世之以道学衣钵自冒。而不能一明其是非之真理者。其可以有省也夫。)批李石谷(圭畯)游支录辨(游支录。日本人德富苏峰猪一郎所作。)
辨曰苏峰之论云孔子之教。文饰太过。故不惟不得收用于当时。亦不可收用于后世。是以后世之人。阳尊阴抑。到处文庙。虽极宏大。而其繁昌反不及关帝娘娘庙之十一。呜乎痛哉。此但见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苏峰既以孔教为文饰太过。则是直以孔教为不善。其诬孔子甚矣。不此之辨。而乃别求所以然何欤。
夫孔子之道。以仁爱为德。以礼让为行。当周之季。诸侯竞争。以诈为贤。以力为能。孔子之道。不见收用。固其所也。
如此为说。是以仁爱礼让。为文饰太过。以实苏峰之言也。岂李氏不达于辞而然耶。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8H 页
 自暴秦以后。以尊君抑臣。为持世之主义。故皆内霸而外王。
自暴秦以后。以尊君抑臣。为持世之主义。故皆内霸而外王。内霸外王者亦绝无。
则孔子之教。为世人之阳尊阴排者。亦不足怪。夫唯阳尊阴排。故到处文庙虽极宏大。而其敬畏繁昌。反不及关君娘娘之庙。势不容不尔。
孔子之道。但主伦常。无许多奇异。故末世之尊之不如他神祠之以祸福动人者耳。使孔庙而得愚夫愚妇之敬畏如关君娘娘之庙。则是亦关君娘娘而已。何以为孔子。
后世所谓儒教者。以阀阅为尊抑之具。
此吾东近代锢弊。国初则未必尽然。况中国则虽屠沽之子。苟材且贤。无不显扬。安得谓后世皆然乎。
以文词为发身之业。
此则隋唐以来皆然。可谓乱政。然究其实则名曰人材。无文词者亦少。
以朋党为权力之关系。
此亦吾东之锢弊。中国未曾如此。
此乃名利之学。非孔子之教本面目。
不知世有何人以是三者。为孔教之本面目者耶。而乃盛气喝骂如此。
苏峰所谓孔子教为政治屋之商标号牌。如达摩之为姻草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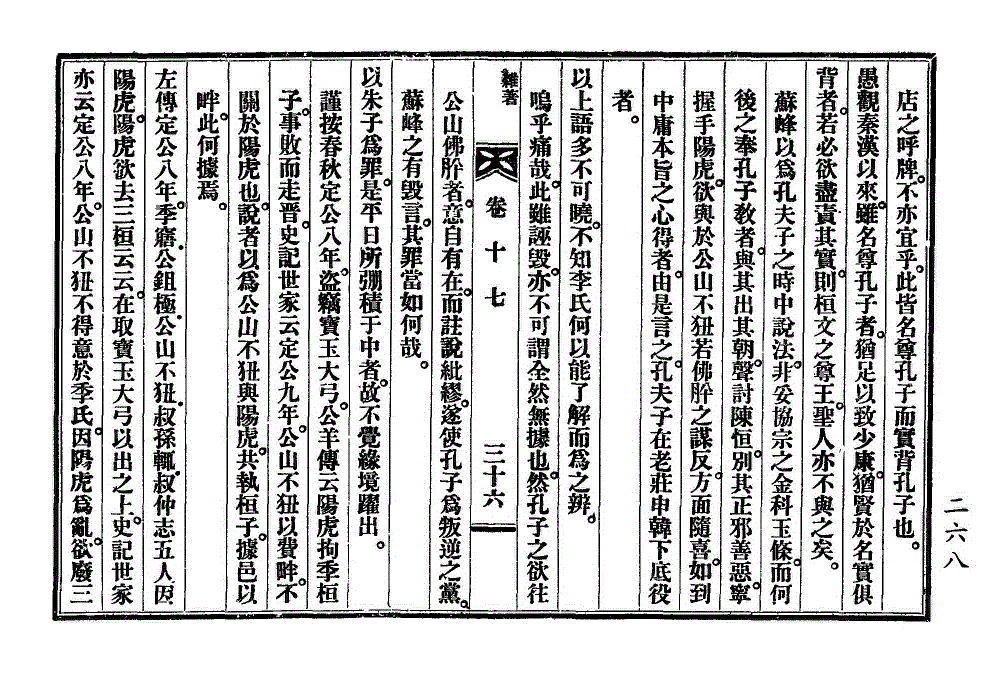 店之呼牌。不亦宜乎。此皆名尊孔子而实背孔子也。
店之呼牌。不亦宜乎。此皆名尊孔子而实背孔子也。愚观秦汉以来。虽名尊孔子者。犹足以致少康。犹贤于名实俱背者。若必欲尽责其实。则桓文之尊王。圣人亦不与之矣。
苏峰以为孔夫子之时中说法。非妥协宗之金科玉条。而何后之奉孔子教者。与其出其朝。声讨陈恒。别其正邪善恶。宁握手阳虎。欲与于公山不狃若佛肸之谋反。方面随喜。如到中庸本旨之心得者。由是言之。孔夫子在老庄申韩下底役者。
以上语多不可晓。不知李氏何以能了解而为之辨。
呜乎痛哉。此虽诬毁。亦不可谓全然无据也。然孔子之欲往公山佛肸者。意自有在。而注说纰缪。遂使孔子为叛逆之党。苏峰之有毁言。其罪当如何哉。
以朱子为罪。是平日所弸积于中者。故不觉缘境跃出。
谨按春秋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公羊传云阳虎拘季桓子。事败而走晋。史记世家云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费畔。不关于阳虎也。说者以为公山不狃与阳虎。共执桓子。据邑以畔。此何据焉。
左传定公八年。季寤,公锄极,公山不狃,叔孙辄,叔仲志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云云。在取宝玉大弓以出之上。史记世家亦云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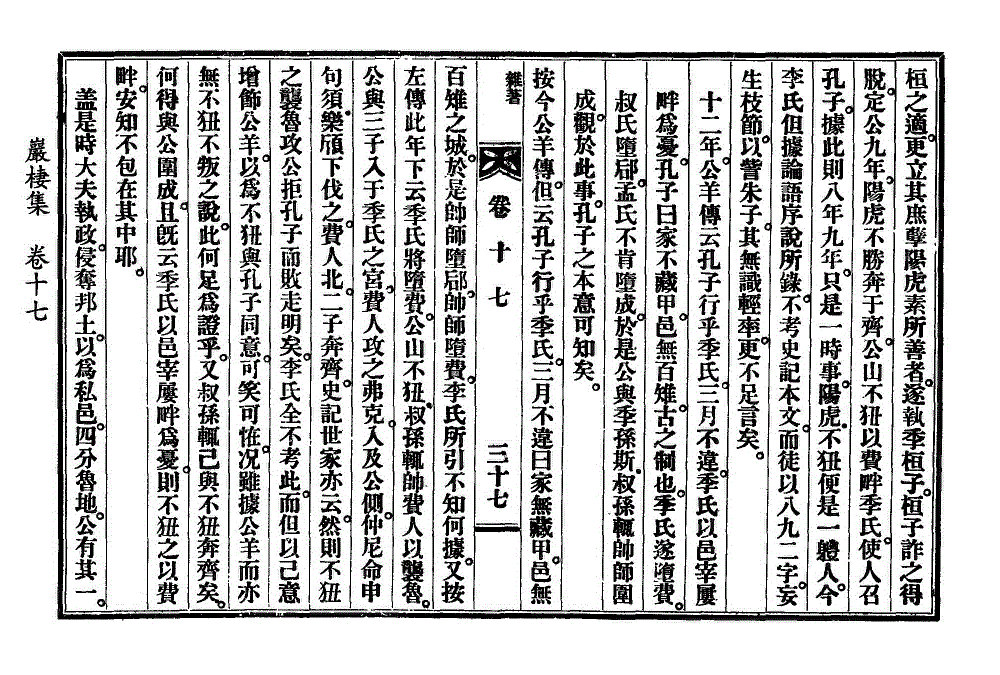 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据此则八年九年。只是一时事。阳虎,不狃便是一体人。今李氏但据论语序说所录。不考史记本文。而徒以八九二字。妄生枝节。以訾朱子。其无识轻率。更不足言矣。
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据此则八年九年。只是一时事。阳虎,不狃便是一体人。今李氏但据论语序说所录。不考史记本文。而徒以八九二字。妄生枝节。以訾朱子。其无识轻率。更不足言矣。十二年。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季氏以邑宰屡畔为忧。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古之制也。季氏遂堕费。叔氏堕郈。孟氏不肯堕成。于是公与季孙斯,叔孙辄帅师围成。观于此事。孔子之本意可知矣。
按今公羊传。但云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曰家无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李氏所引不知何据。又按左传此年下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史记世家亦云。然则不狃之袭鲁攻公拒孔子而败走明矣。李氏全不考此。而但以己意增饰公羊。以为不狃与孔子同意。可笑可怪。况虽据公羊而亦无不狃不叛之说。此何足为證乎。又叔孙辄已与不狃奔齐矣。何得与公围成。且既云季氏以邑宰屡畔为忧。则不狃之以费畔。安知不包在其中耶。
盖是时大夫执政。侵夺邦土。以为私邑。四分鲁地。公有其一。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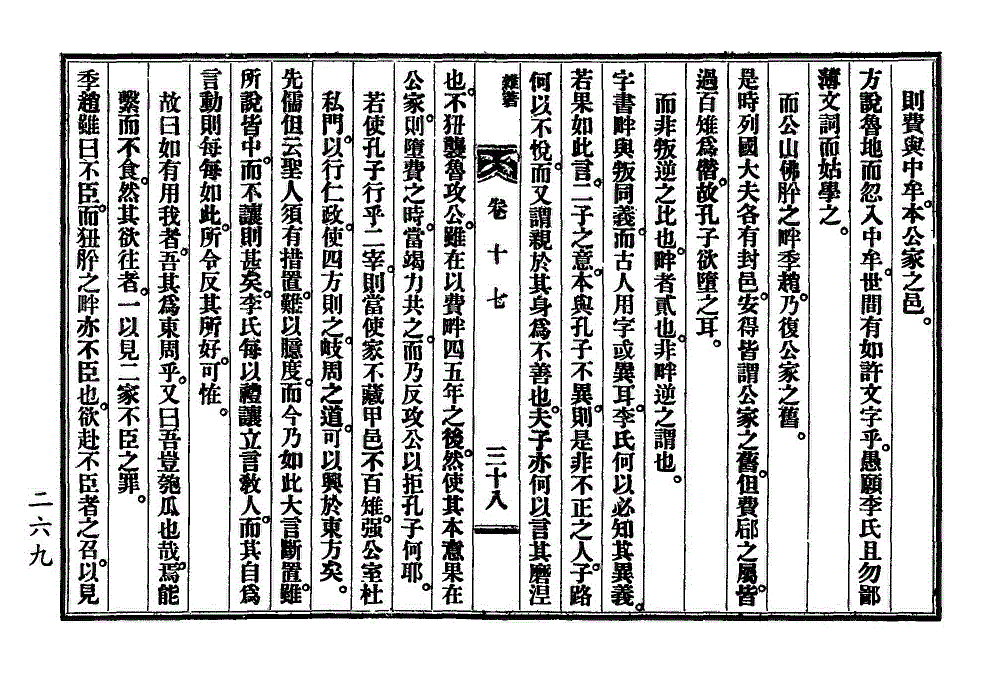 则费与中牟。本公家之邑。
则费与中牟。本公家之邑。方说鲁地而忽入中牟。世间有如许文字乎。愚愿李氏且勿鄙薄文词而姑学之。
而公山佛肸之畔季赵。乃复公家之旧。
是时列国大夫各有封邑。安得皆谓公家之旧。但费郈之属。皆过百雉为僭。故孔子欲堕之耳。
而非叛逆之比也。畔者贰也。非畔逆之谓也。
字书畔与叛同义。而古人用字或异耳。李氏何以必知其异义。若果如此言。二子之意。本与孔子不异。则是非不正之人。子路何以不悦。而又谓亲于其身为不善也。夫子亦何以言其磨涅也。不狃袭鲁攻公。虽在以费畔四五年之后。然使其本意果在公家。则堕费之时。当竭力共之。而乃反攻公以拒孔子何耶。
若使孔子行乎二宰。则当使家不藏甲邑不百雉。强公室杜私门。以行仁政。使四方则之。岐周之道。可以兴于东方矣。
先儒但云圣人须有措置。难以臆度。而今乃如此大言断置。虽所说皆中。而不让则甚矣。李氏每以礼让立言教人。而其自为言动则每每如此。所令反其所好。可怪。
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然其欲往者。一以见二家不臣之罪。
季赵虽曰不臣。而狃肸之畔亦不臣也。欲赴不臣者之召。以见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0H 页
 不臣者之罪。圣人之心。果如是崎岖迂僻乎。
不臣者之罪。圣人之心。果如是崎岖迂僻乎。一以见吾道可行之兆耳。
未尝往而何以遂见可行之兆。
其终不往者。如浮海之叹也。
固如浮海之叹。然子路之喜于彼而不悦于此者何也。试思之。
其说曰圣人无不可为之人。亦无不可为之事。若使圣人无不可为之人。是不知人也。无不可为之事则非时中也。
集注下段亦有知其人之终不可变事之终不可为之语也。李氏之眼。何以独明于上句而瞽于下句也。岂其仇视朱子之祟。根于肝脏。故目受其害也耶。
孔子不见阳虎。
不狃,佛肸亦未尝见也。若言其可见则孟子固曰阳货先。安得不见云尔。
不从弥子瑕。
弥子瑕之欲孔子主己。不过以要荣宠而已。其可为与不可为。非所举论。此等并混杂言之。粗率甚矣。
则是无不可为之人乎。
集注所谓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二句。真写得圣人胸怀出。若当初以为不可为而绝之。则是晨门沮溺之所为。岂足为孔子。然当时如荷蒉等异人。犹不知此意。岂后世庸人所及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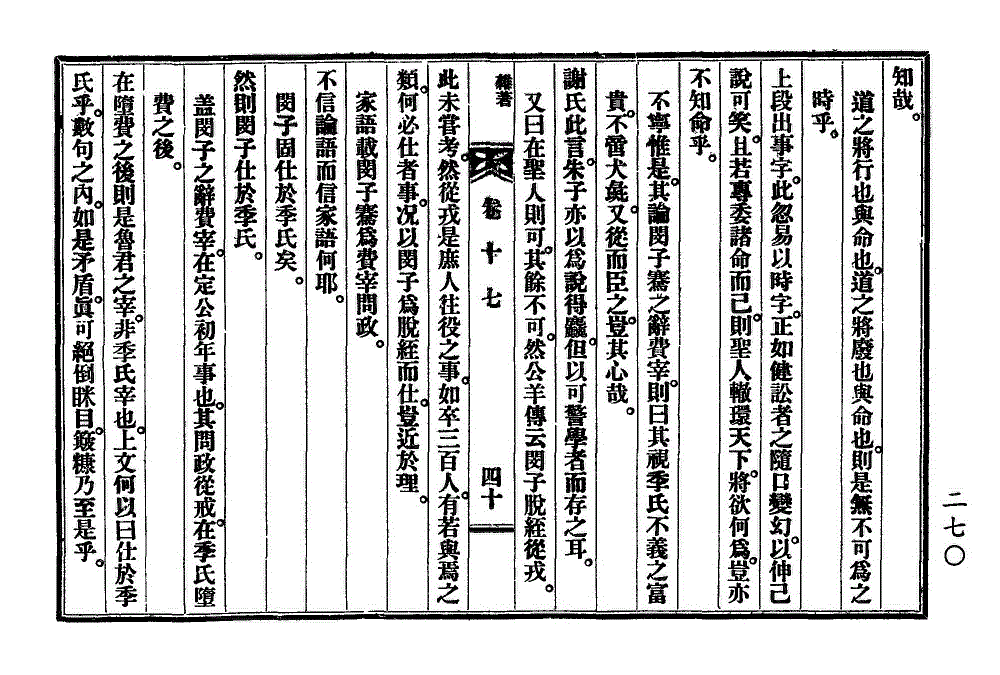 知哉。
知哉。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则是无不可为之时乎。
上段出事字。此忽易以时字。正如健讼者之随口变幻。以伸己说可笑。且若专委诸命而已。则圣人辙环天下。将欲何为。岂亦不知命乎。
不宁惟是。其论闵子骞之辞费宰。则曰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不啻犬彘。又从而臣之。岂其心哉。
谢氏此言。朱子亦以为说得粗。但以可警学者而存之耳。
又曰在圣人则可。其馀不可。然公羊传云闵子脱绖从戎。
此未尝考。然从戎是庶人往役之事。如卒三百人。有若与焉之类。何必仕者事。况以闵子为脱绖而仕。岂近于理。
家语载闵子骞为费宰问政。
不信论语而信家语何耶。
闵子固仕于季氏矣。
然则闵子仕于季氏。
盖闵子之辞费宰。在定公初年事也。其问政从戒。在季氏堕费之后。
在堕费之后则是鲁君之宰。非季氏宰也。上文何以曰仕于季氏乎。数句之内。如是矛盾。真可绝倒眯目。簸糠乃至是乎。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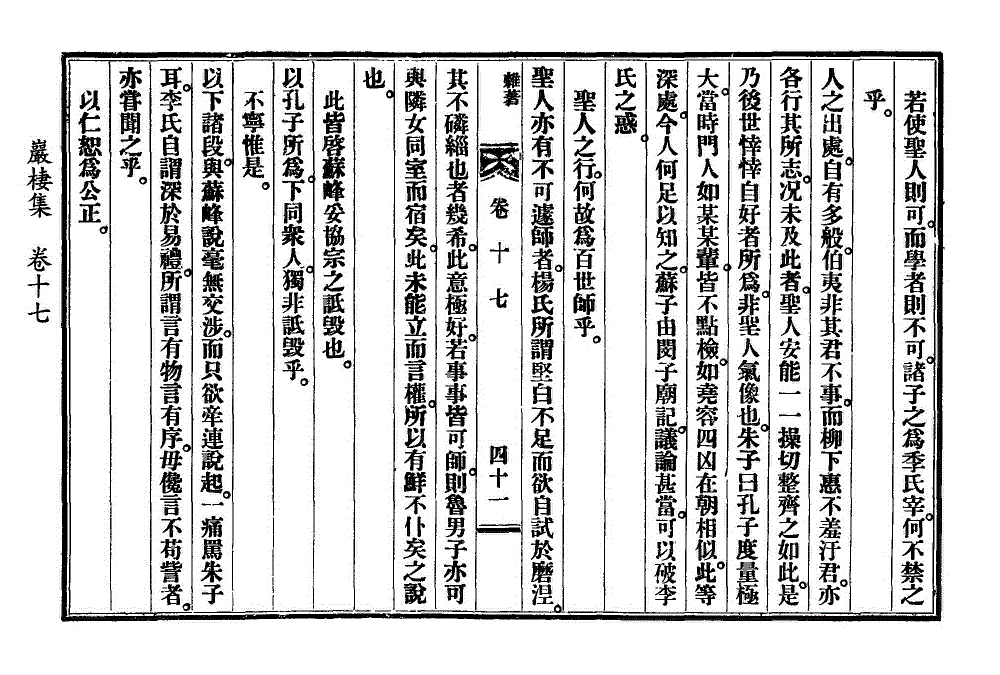 若使圣人则可。而学者则不可。诸子之为季氏宰。何不禁之乎。
若使圣人则可。而学者则不可。诸子之为季氏宰。何不禁之乎。人之出处。自有多般。伯夷非其君不事。而柳下惠不羞污君。亦各行其所志。况未及此者。圣人安能一一操切整齐之如此。是乃后世悻悻自好者所为。非圣人气像也。朱子曰孔子度量极大。当时门人如某某辈。皆不点检。如尧容四凶在朝相似。此等深处。今人何足以知之。苏子由闵子庙记。议论甚当。可以破李氏之惑。
圣人之行。何故为百世师乎。
圣人亦有不可遽师者。杨氏所谓坚白不足而欲自试于磨涅。其不磷缁也者几希。此意极好。若事事皆可师。则鲁男子亦可与邻女同室而宿矣。此未能立而言权。所以有鲜不仆矣之说也。
此皆启苏峰妥协宗之诋毁也。
以孔子所为。下同众人。独非诋毁乎。
不宁惟是。
以下诸段。与苏峰说毫无交涉。而只欲牵连说起。一痛骂朱子耳。李氏自谓深于易礼。所谓言有物言有序。毋儳言不苟訾者。亦尝闻之乎。
以仁恕为公正。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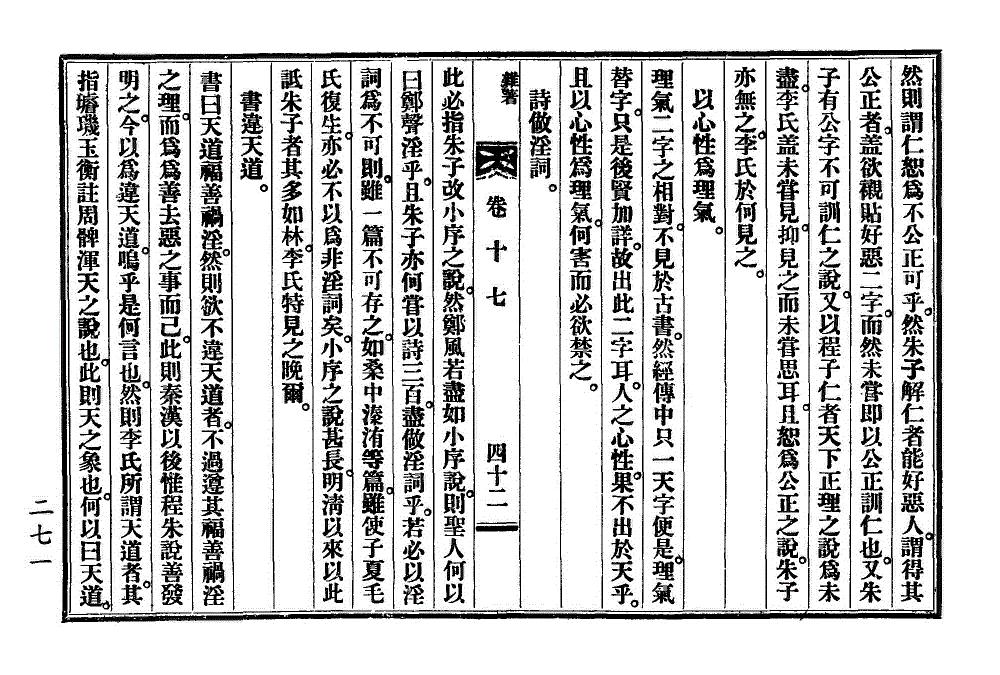 然则谓仁恕为不公正可乎。然朱子解仁者能好恶人。谓得其公正者。盖欲衬贴好恶二字。而然未尝即以公正训仁也。又朱子有公字不可训仁之说。又以程子仁者天下正理之说为未尽。李氏盖未尝见。抑见之而未尝思耳。且恕为公正之说。朱子亦无之。李氏于何见之。
然则谓仁恕为不公正可乎。然朱子解仁者能好恶人。谓得其公正者。盖欲衬贴好恶二字。而然未尝即以公正训仁也。又朱子有公字不可训仁之说。又以程子仁者天下正理之说为未尽。李氏盖未尝见。抑见之而未尝思耳。且恕为公正之说。朱子亦无之。李氏于何见之。以心性为理气。
理气二字之相对。不见于古书。然经传中只一天字便是。理气替字。只是后贤加详。故出此二字耳。人之心性。果不出于天乎。且以心性为理气。何害而必欲禁之。
诗做淫词。
此必指朱子改小序之说。然郑风若尽如小序说。则圣人何以曰郑声淫乎。且朱子亦何尝以诗三百。尽做淫词乎。若必以淫词为不可则。虽一篇不可存之。如桑中溱洧等篇。虽使子夏毛氏复生。亦必不以为非淫词矣。小序之说甚长。明清以来以此诋朱子者其多如林。李氏特见之晚尔。
书违天道。
书曰天道福善祸淫。然则欲不违天道者。不过遵其福善祸淫之理。而为为善去恶之事而已。此则秦汉以后惟程朱说善发明之。今以为违天道。呜乎是何言也。然则李氏所谓天道者。其指璿玑玉衡注周髀浑天之说也。此则天之象也。何以曰天道。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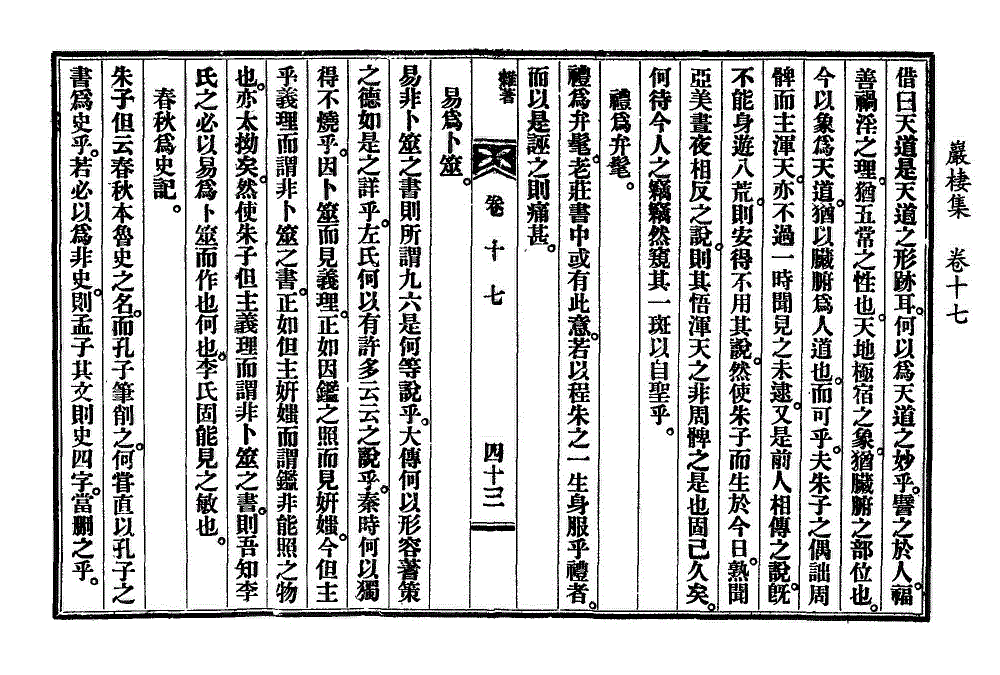 借曰天道是天道之形迹耳。何以为天道之妙乎。譬之于人。福善祸淫之理。犹五常之性也。天地极宿之象。犹脏腑之部位也。今以象为天道。犹以脏腑为人道也。而可乎。夫朱子之偶诎周髀而主浑天。亦不过一时闻见之未逮。又是前人相传之说。既不能身游八荒。则安得不用其说。然使朱子而生于今日。熟闻亚美昼夜相反之说。则其悟浑天之非周髀之是也固已久矣。何待今人之窃窃然窥其一斑以自圣乎。
借曰天道是天道之形迹耳。何以为天道之妙乎。譬之于人。福善祸淫之理。犹五常之性也。天地极宿之象。犹脏腑之部位也。今以象为天道。犹以脏腑为人道也。而可乎。夫朱子之偶诎周髀而主浑天。亦不过一时闻见之未逮。又是前人相传之说。既不能身游八荒。则安得不用其说。然使朱子而生于今日。熟闻亚美昼夜相反之说。则其悟浑天之非周髀之是也固已久矣。何待今人之窃窃然窥其一斑以自圣乎。礼为弁髦。
礼为弁髦。老庄书中或有此意。若以程朱之一生身服乎礼者。而以是诬之则痛甚。
易为卜筮。
易非卜筮之书则所谓九六是何等说乎。大传何以形容蓍策之德如是之详乎。左氏何以有许多云云之说乎。秦时何以独得不烧乎。因卜筮而见义理。正如因鉴之照而见妍媸。今但主乎义理而谓非卜筮之书。正如但主妍媸而谓鉴非能照之物也。亦太拗矣。然使朱子但主义理而谓非卜筮之书。则吾知李氏之必以易为卜筮而作也何也。李氏固能见之敏也。
春秋为史记。
朱子但云春秋本鲁史之名。而孔子笔削之。何尝直以孔子之书为史乎。若必以为非史。则孟子其文则史四字。当删之乎。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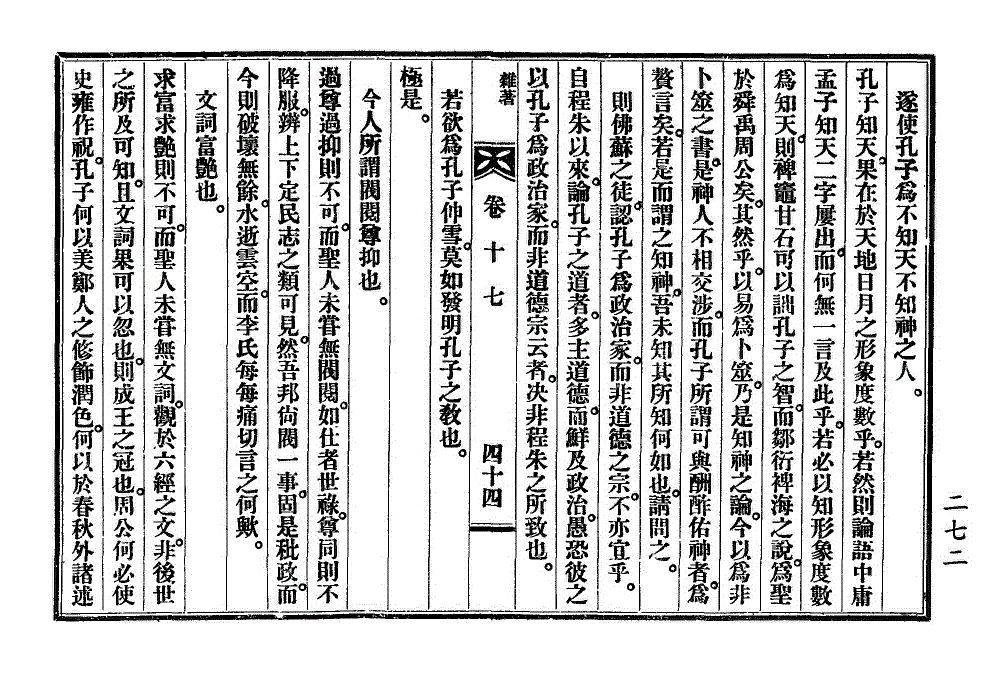 遂使孔子为不知天不知神之人。
遂使孔子为不知天不知神之人。孔子知天。果在于天地日月之形象度数乎。若然则论语中庸孟子知天二字屡出。而何无一言及此乎。若必以知形象度数为知天。则裨灶甘石可以诎孔子之智。而邹衍裨海之说。为圣于舜禹周公矣。其然乎。以易为卜筮。乃是知神之论。今以为非卜筮之书。是神人不相交涉。而孔子所谓可与酬酢佑神者。为赘言矣。若是而谓之知神。吾未知其所知何如也。请问之。
则佛苏之徒。认孔子为政治家。而非道德之宗。不亦宜乎。
自程朱以来。论孔子之道者。多主道德。而鲜及政治。愚恐彼之以孔子为政治家。而非道德宗云者。决非程朱之所致也。
若欲为孔子伸雪。莫如发明孔子之教也。
极是。
今人所谓阀阅尊抑也。
过尊过抑则不可。而圣人未尝无阀阅。如仕者世禄。尊同则不降服。辨上下定民志之类可见。然吾邦尚阀一事。固是秕政。而今则破坏无馀。水逝云空。而李氏每每痛切言之何欤。
文词富艳也。
求富求艳则不可。而圣人未尝无文词。观于六经之文。非后世之所及可知。且文词果可以忽也。则成王之冠也。周公何必使史雍作祝。孔子何以美郑人之修饰润色。何以于春秋外诸述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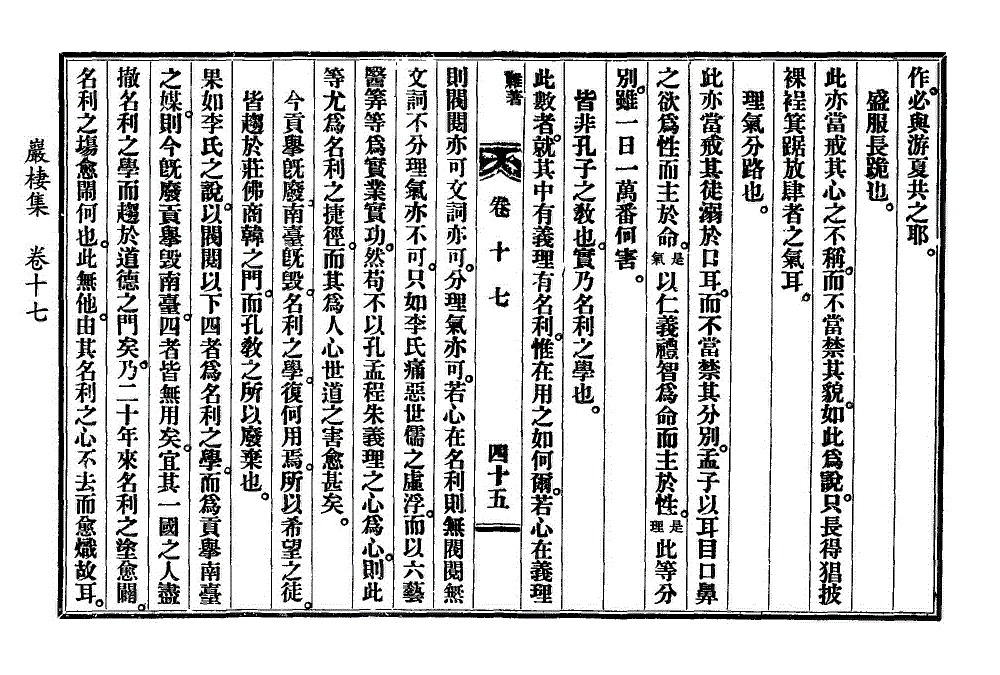 作。必与游夏共之耶。
作。必与游夏共之耶。盛服长跪也。
此亦当戒其心之不称。而不当禁其貌。如此为说。只长得猖披裸裎箕踞放肆者之气耳。
理气分路也。
此亦当戒其徒溺于口耳。而不当禁其分别。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欲为性而主于命。(是气)以仁义礼智为命而主于性。(是理)此等分别。虽一日一万番何害。
皆非孔子之教也。实乃名利之学也。
此数者。就其中有义理有名利。惟在用之如何尔。若心在义理则阀阅亦可文词亦可。分理气亦可。若心在名利则无阀阅无文词不分理气亦不可。只如李氏痛恶世儒之虚浮。而以六艺医算等为实业实功。然苟不以孔孟程朱义理之心为心。则此等尤为名利之捷径。而其为人心世道之害愈甚矣。
今贡举既废。南台既毁。名利之学。复何用焉。所以希望之徒。皆趋于庄佛商韩之门。而孔教之所以废弃也。
果如李氏之说。以阀阅以下四者为名利之学。而为贡举南台之媒。则今既废贡举毁南台。四者皆无用矣。宜其一国之人尽撤名利之学而趋于道德之门矣。乃二十年来名利之涂愈辟。名利之场愈闹何也。此无他。由其名利之心不去而愈炽故耳。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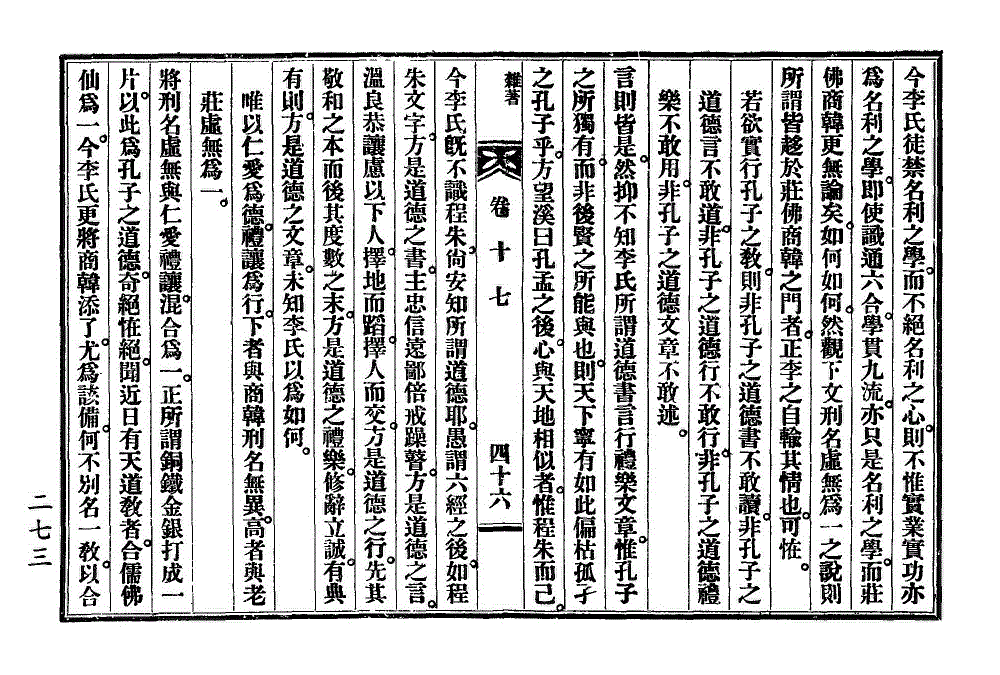 今李氏徒禁名利之学。而不绝名利之心。则不惟实业实功亦为名利之学。即使识通六合。学贯九流。亦只是名利之学。而庄佛商韩更无论矣。如何如何。然观下文刑名虚无为一之说则所谓皆趍于庄佛商韩之门者。正李之自输其情也。可怪。
今李氏徒禁名利之学。而不绝名利之心。则不惟实业实功亦为名利之学。即使识通六合。学贯九流。亦只是名利之学。而庄佛商韩更无论矣。如何如何。然观下文刑名虚无为一之说则所谓皆趍于庄佛商韩之门者。正李之自输其情也。可怪。若欲实行孔子之教。则非孔子之道德书不敢读。非孔子之道德言不敢道。非孔子之道德行不敢行。非孔子之道德礼乐不敢用。非孔子之道德文章不敢述。
言则皆是。然抑不知李氏所谓道德书言行礼乐文章。惟孔子之所独有。而非后贤之所能与也。则天下宁有如此偏枯孤孑之孔子乎。方望溪曰孔孟之后。心与天地相似者。惟程朱而已。今李氏既不识程朱。尚安知所谓道德耶。愚谓六经之后。如程朱文字。方是道德之书。主忠信远鄙倍戒躁瞽。方是道德之言。温良恭让虑以下人。择地而蹈。择人而交。方是道德之行。先其敬和之本而后其度数之末。方是道德之礼乐。修辞立诚。有典有则。方是道德之文章。未知李氏以为如何。
唯以仁爱为德。礼让为行。下者与商韩刑名无异。高者与老庄虚无为一。
将刑名虚无与仁爱礼让。混合为一。正所谓铜铁金银打成一片。以此为孔子之道德。奇绝怪绝。闻近日有天道教者。合儒佛仙为一。今李氏更将商韩添了。尤为该备。何不别名一教。以合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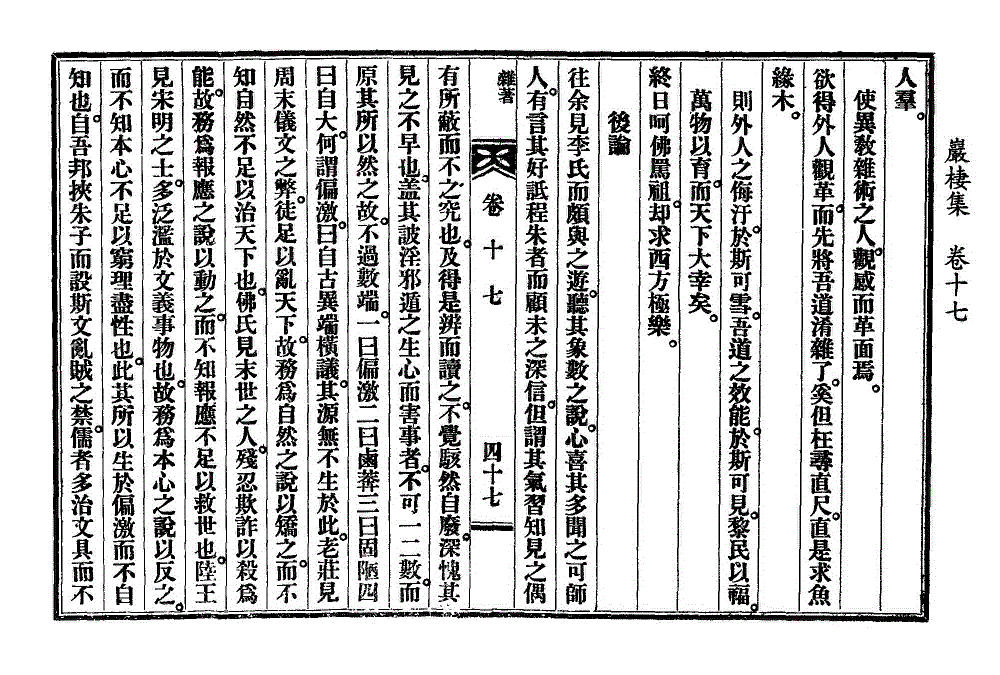 人群。
人群。使异教杂术之人。观感而革面焉。
欲得外人观革。而先将吾道淆杂了。奚但枉寻直尺。直是求鱼缘木。
则外人之侮污。于斯可雪。吾道之效能。于斯可见。黎民以福。万物以育。而天下大幸矣。
终日呵佛骂祖。却求西方极乐。
后论
往余见李氏而颇与之游。听其象数之说。心喜其多闻之可师人。有言其好诋程朱者而顾未之深信。但谓其气习知见之偶有所蔽而不之究也。及得是辨而读之。不觉骇然自废。深愧其见之不早也。盖其诐淫邪遁之生心而害事者。不可一二数。而原其所以然之故。不过数端。一曰偏激二曰卤莽三曰固陋四曰自大。何谓偏激。曰自古异端横议。其源无不生于此。老庄见周末仪文之弊。徒足以乱天下。故务为自然之说以矫之。而不知自然不足以治天下也。佛氏见末世之人。残忍欺诈以杀为能。故务为报应之说以动之。而不知报应不足以救世也。陆王见宋明之士。多泛滥于文义事物也。故务为本心之说以反之。而不知本心不足以穷理尽性也。此其所以生于偏激而不自知也。自吾邦挟朱子而设斯文乱贼之禁。儒者多治文具而不
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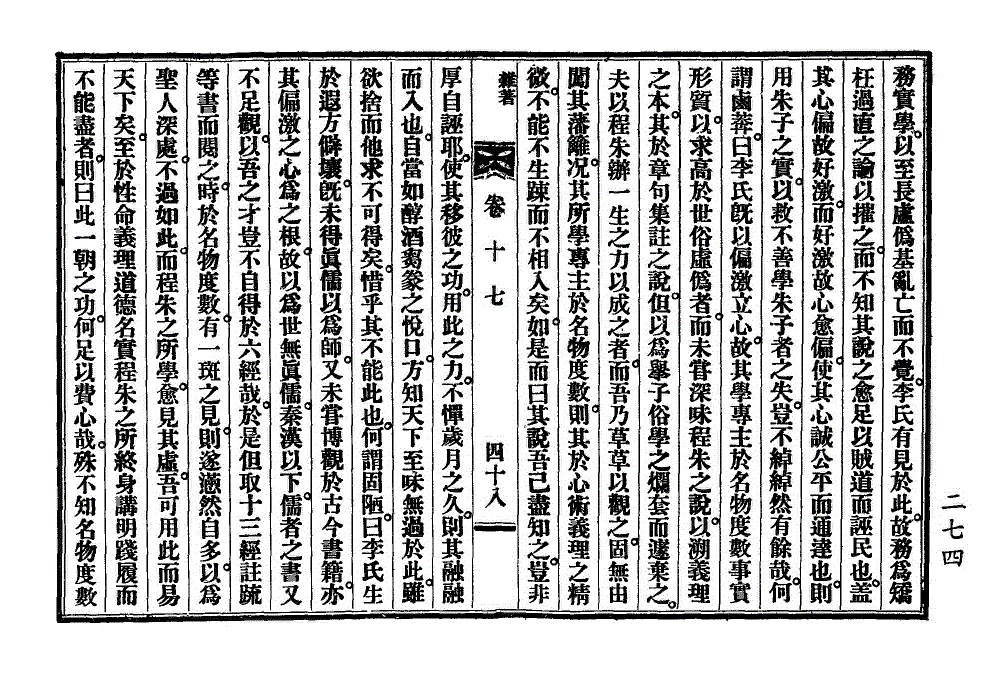 务实学。以至长虚伪基乱亡而不觉。李氏有见于此。故务为矫枉过直之论以摧之。而不知其说之愈足以贼道而诬民也。盖其心偏故好激。而好激故心愈偏。使其心诚公平而通达也。则用朱子之实。以救不善学朱子者之失。岂不绰绰然有馀哉。何谓卤莽。曰李氏既以偏激立心。故其学专主于名物度数事实形质。以求高于世俗虚伪者。而未尝深味程朱之说。以溯义理之本。其于章句集注之说。但以为举子俗学之烂套而遽弃之。夫以程朱办一生之力以成之者。而吾乃草草以观之。固无由闯其藩篱。况其所学专主于名物度数。则其于心术义理之精微。不能不生疏而不相入矣。如是而曰其说吾已尽知之。岂非厚自诬耶。使其移彼之功。用此之力。不惮岁月之久。则其融融而入也。自当如醇酒刍豢之悦口。方知天下至味无过于此。虽欲舍而他求不可得矣。惜乎其不能此也。何谓固陋。曰李氏生于遐方僻壤。既未得真儒以为师。又未尝博观于古今书籍。亦其偏激之心为之根。故以为世无真儒。秦汉以下。儒者之书又不足观。以吾之才岂不自得于六经哉。于是但取十三经注疏等书而阅之。时于名物度数。有一斑之见。则遂懑然自多。以为圣人深处。不过如此。而程朱之所学。愈见其虚。吾可用此而易天下矣。至于性命义理道德名实程朱之所终身讲明践履而不能尽者。则曰此一朝之功。何足以费心哉。殊不知名物度数
务实学。以至长虚伪基乱亡而不觉。李氏有见于此。故务为矫枉过直之论以摧之。而不知其说之愈足以贼道而诬民也。盖其心偏故好激。而好激故心愈偏。使其心诚公平而通达也。则用朱子之实。以救不善学朱子者之失。岂不绰绰然有馀哉。何谓卤莽。曰李氏既以偏激立心。故其学专主于名物度数事实形质。以求高于世俗虚伪者。而未尝深味程朱之说。以溯义理之本。其于章句集注之说。但以为举子俗学之烂套而遽弃之。夫以程朱办一生之力以成之者。而吾乃草草以观之。固无由闯其藩篱。况其所学专主于名物度数。则其于心术义理之精微。不能不生疏而不相入矣。如是而曰其说吾已尽知之。岂非厚自诬耶。使其移彼之功。用此之力。不惮岁月之久。则其融融而入也。自当如醇酒刍豢之悦口。方知天下至味无过于此。虽欲舍而他求不可得矣。惜乎其不能此也。何谓固陋。曰李氏生于遐方僻壤。既未得真儒以为师。又未尝博观于古今书籍。亦其偏激之心为之根。故以为世无真儒。秦汉以下。儒者之书又不足观。以吾之才岂不自得于六经哉。于是但取十三经注疏等书而阅之。时于名物度数。有一斑之见。则遂懑然自多。以为圣人深处。不过如此。而程朱之所学。愈见其虚。吾可用此而易天下矣。至于性命义理道德名实程朱之所终身讲明践履而不能尽者。则曰此一朝之功。何足以费心哉。殊不知名物度数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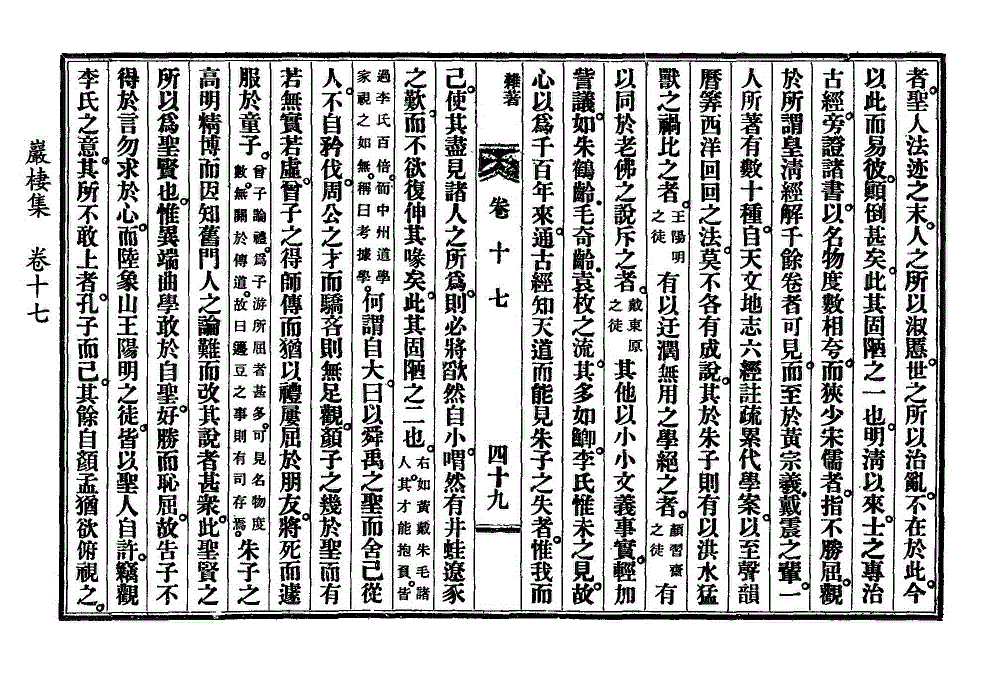 者。圣人法迹之末。人之所以淑慝。世之所以治乱。不在于此。今以此而易彼。颠倒甚矣。此其固陋之一也。明清以来。士之专治古经。旁證诸书。以名物度数相夸。而狭少宋儒者。指不胜屈。观于所谓皇清经解千馀卷者可见。而至于黄宗羲,戴震之辈。一人所著有数十种。自天文地志六经注疏累代学案。以至声韵历算西洋回回之法。莫不各有成说。其于朱子则有以洪水猛兽之祸比之者。(王阳明之徒)有以迂阔无用之学绝之者。(颜习斋之徒)有以同于老佛之说斥之者。(戴东原之徒)其他以小小文义事实。轻加訾议。如朱鹤龄,毛奇龄,袁枚之流。其多如鲫。李氏惟未之见。故心以为千百年来。通古经知天道而能见朱子之失者。惟我而已。使其尽见诸人之所为。则必将欿然自小。喟然有井蛙辽豕之叹。而不欲复伸其喙矣。此其固陋之二也。(右如黄戴朱毛诸人。其才能抱负。皆过李氏百倍。而中州道学家视之如无。称曰考据学。)何谓自大。曰以舜禹之圣而舍己从人。不自矜伐。周公之才而骄吝则无足观。颜子之几于圣而有若无实若虚。曾子之得师传而犹以礼屡屈于朋友。将死而遽服于童子。(曾子论礼。为子游所屈者甚多。可见名物度数。无关于传道。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焉。)朱子之高明精博而因知旧门人之论难而改其说者甚众。此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惟异端曲学敢于自圣。好胜而耻屈。故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陆象山王阳明之徒。皆以圣人自许。窃观李氏之意。其所不敢上者。孔子而已。其馀自颜孟犹欲俯视之。
者。圣人法迹之末。人之所以淑慝。世之所以治乱。不在于此。今以此而易彼。颠倒甚矣。此其固陋之一也。明清以来。士之专治古经。旁證诸书。以名物度数相夸。而狭少宋儒者。指不胜屈。观于所谓皇清经解千馀卷者可见。而至于黄宗羲,戴震之辈。一人所著有数十种。自天文地志六经注疏累代学案。以至声韵历算西洋回回之法。莫不各有成说。其于朱子则有以洪水猛兽之祸比之者。(王阳明之徒)有以迂阔无用之学绝之者。(颜习斋之徒)有以同于老佛之说斥之者。(戴东原之徒)其他以小小文义事实。轻加訾议。如朱鹤龄,毛奇龄,袁枚之流。其多如鲫。李氏惟未之见。故心以为千百年来。通古经知天道而能见朱子之失者。惟我而已。使其尽见诸人之所为。则必将欿然自小。喟然有井蛙辽豕之叹。而不欲复伸其喙矣。此其固陋之二也。(右如黄戴朱毛诸人。其才能抱负。皆过李氏百倍。而中州道学家视之如无。称曰考据学。)何谓自大。曰以舜禹之圣而舍己从人。不自矜伐。周公之才而骄吝则无足观。颜子之几于圣而有若无实若虚。曾子之得师传而犹以礼屡屈于朋友。将死而遽服于童子。(曾子论礼。为子游所屈者甚多。可见名物度数。无关于传道。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焉。)朱子之高明精博而因知旧门人之论难而改其说者甚众。此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惟异端曲学敢于自圣。好胜而耻屈。故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陆象山王阳明之徒。皆以圣人自许。窃观李氏之意。其所不敢上者。孔子而已。其馀自颜孟犹欲俯视之。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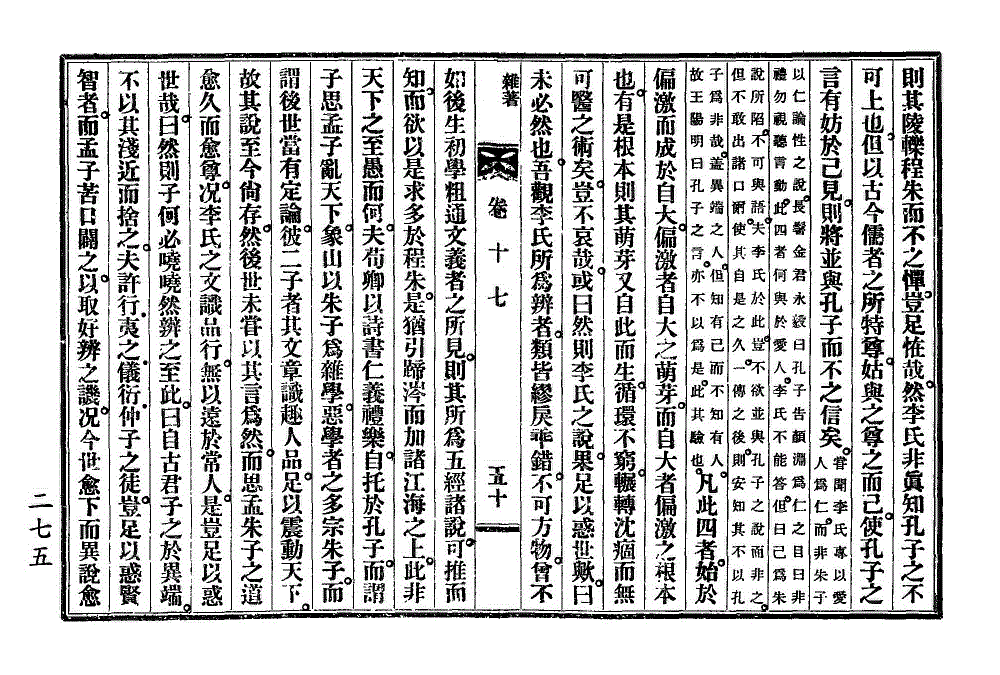 则其陵轹程朱而不之惮。岂足怪哉。然李氏非真知孔子之不可上也。但以古今儒者之所特尊。姑与之尊之而已。使孔子之言有妨于己见。则将并与孔子而不之信矣。(尝闻李氏专以爱人为仁。而非朱子以仁论性之说。长鬐金君永毅曰孔子告颜渊为仁之目曰非礼勿视听言动。此四者何与于爱人。李氏不能答。但曰已为朱说所陷。不可与语。夫李氏于此。岂不欲并与孔子之说而非之。但不敢出诸口尔。使其自是之久。一传之后。则安知其不以孔子为非哉。盖异端之人。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王阳明曰孔子之言。亦不以为是。此其验也。)凡此四者。始于偏激而成于自大。偏激者自大之萌芽。而自大者偏激之根本也。有是根本则其萌芽又自此而生。循环不穷。辗转沈痼而无可医之术矣。岂不哀哉。或曰然则李氏之说。果足以惑世欤。曰未必然也。吾观李氏所为辨者。类皆缪戾乖错。不可方物。曾不如后生初学粗通文义者之所见。则其所为五经诸说。可推而知。而欲以是求多于程朱。是犹引蹄涔而加诸江海之上。此非天下之至愚而何。夫苟卿以诗书仁义礼乐。自托于孔子。而谓子思孟子乱天下。象山以朱子为杂学。恶学者之多宗朱子。而谓后世当有定论。彼二子者其文章识趣人品。足以震动天下。故其说至今尚存。然后世未尝以其言为然。而思孟朱子之道愈久而愈尊。况李氏之文识品行。无以远于常人。是岂足以惑世哉。曰然则子何必哓哓然辨之至此。曰自古君子之于异端。不以其浅近而舍之。夫许行,夷之,仪衍,仲子之徒。岂足以惑贤智者。而孟子苦口辟之。以取好辨之讥。况今世愈下而异说愈
则其陵轹程朱而不之惮。岂足怪哉。然李氏非真知孔子之不可上也。但以古今儒者之所特尊。姑与之尊之而已。使孔子之言有妨于己见。则将并与孔子而不之信矣。(尝闻李氏专以爱人为仁。而非朱子以仁论性之说。长鬐金君永毅曰孔子告颜渊为仁之目曰非礼勿视听言动。此四者何与于爱人。李氏不能答。但曰已为朱说所陷。不可与语。夫李氏于此。岂不欲并与孔子之说而非之。但不敢出诸口尔。使其自是之久。一传之后。则安知其不以孔子为非哉。盖异端之人。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王阳明曰孔子之言。亦不以为是。此其验也。)凡此四者。始于偏激而成于自大。偏激者自大之萌芽。而自大者偏激之根本也。有是根本则其萌芽又自此而生。循环不穷。辗转沈痼而无可医之术矣。岂不哀哉。或曰然则李氏之说。果足以惑世欤。曰未必然也。吾观李氏所为辨者。类皆缪戾乖错。不可方物。曾不如后生初学粗通文义者之所见。则其所为五经诸说。可推而知。而欲以是求多于程朱。是犹引蹄涔而加诸江海之上。此非天下之至愚而何。夫苟卿以诗书仁义礼乐。自托于孔子。而谓子思孟子乱天下。象山以朱子为杂学。恶学者之多宗朱子。而谓后世当有定论。彼二子者其文章识趣人品。足以震动天下。故其说至今尚存。然后世未尝以其言为然。而思孟朱子之道愈久而愈尊。况李氏之文识品行。无以远于常人。是岂足以惑世哉。曰然则子何必哓哓然辨之至此。曰自古君子之于异端。不以其浅近而舍之。夫许行,夷之,仪衍,仲子之徒。岂足以惑贤智者。而孟子苦口辟之。以取好辨之讥。况今世愈下而异说愈岩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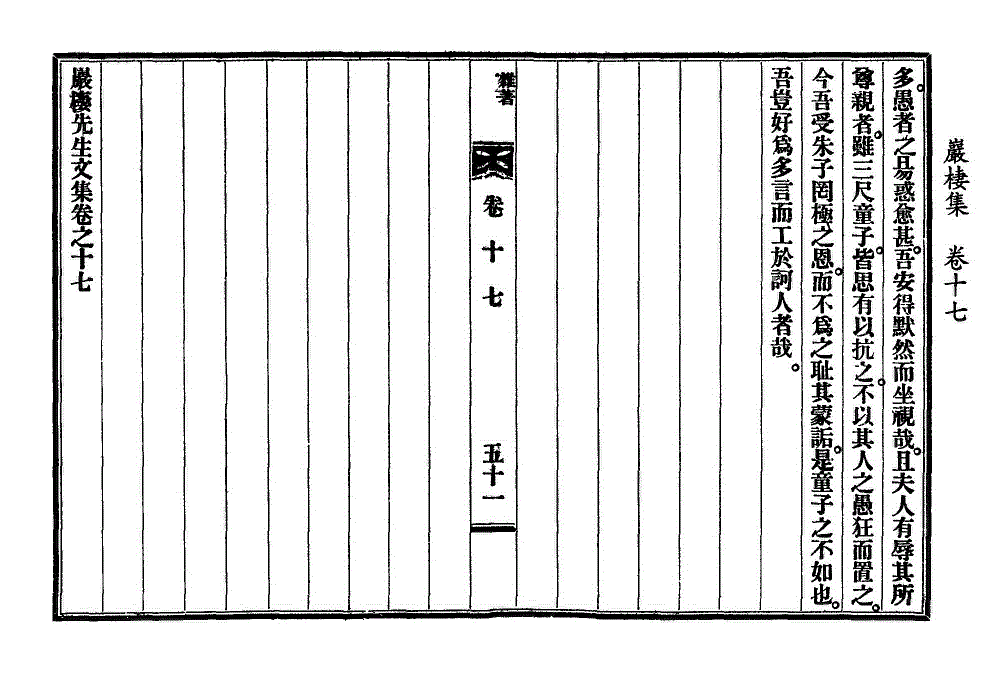 多。愚者之易惑愈甚。吾安得默然而坐视哉。且夫人有辱其所尊亲者。虽三尺童子。皆思有以抗之。不以其人之愚狂而置之。今吾受朱子罔极之恩。而不为之耻其蒙诟。是童子之不如也。吾岂好为多言而工于诃人者哉。
多。愚者之易惑愈甚。吾安得默然而坐视哉。且夫人有辱其所尊亲者。虽三尺童子。皆思有以抗之。不以其人之愚狂而置之。今吾受朱子罔极之恩。而不为之耻其蒙诟。是童子之不如也。吾岂好为多言而工于诃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