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x 页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疏
疏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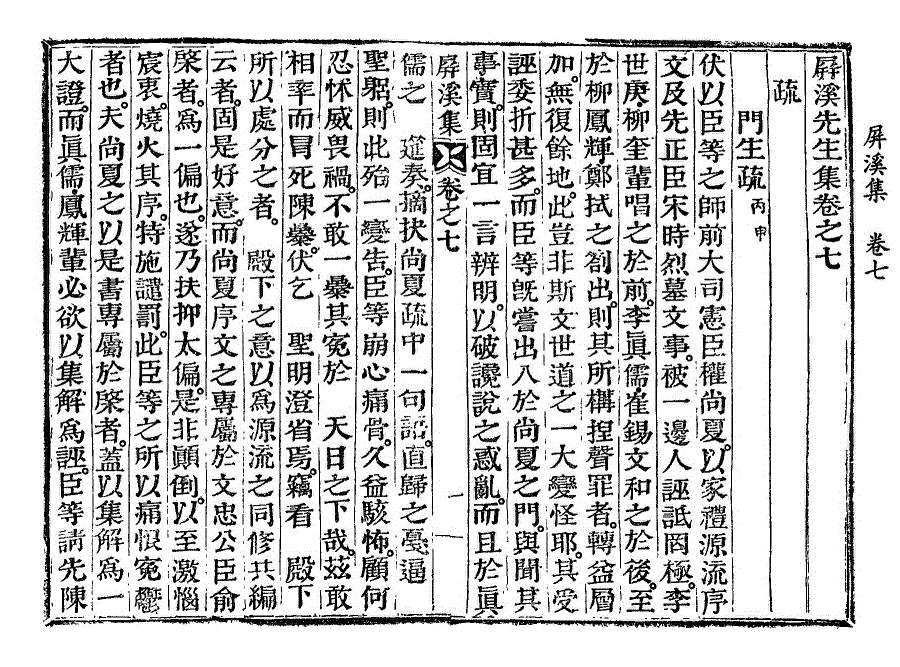 门生疏(丙申)
门生疏(丙申)伏以臣等之师前大司宪臣权尚夏。以家礼源流序文及先正臣宋时烈墓文事。被一边人诬诋罔极。李世庚,柳奎辈唱之于前。李真儒,崔锡文和之于后。至于柳凤辉,郑拭之劄出。则其所构捏声罪者。转益层加。无复馀地。此岂非斯文世道之一大变怪耶。其受诬委折甚多。而臣等既尝出入于尚夏之门。与闻其事实。则固宜一言辨明。以破谗说之惑乱。而且于真儒之 筵奏。摘抉尚夏疏中一句语。直归之戛逼 圣躬。则此殆一变告。臣等崩心痛骨。久益骇怖。顾何忍怵威畏祸。不敢一㬥其冤于 天日之下哉。兹敢相率而冒死陈㬥。伏乞 圣明澄省焉。窃看 殿下所以处分之者。 殿下之意以为源流之同修共编云者。固是好意。而尚夏序文之专属于文忠公臣俞棨者。为一偏也。遂乃扶抑太偏。是非颠倒。以至激恼宸衷。烧火其序。特施谴罚。此臣等之所以痛恨冤郁者也。夫尚夏之以是书专属于棨者。盖以集解为一大證。而真儒,凤辉辈必欲以集解为诬。臣等请先陈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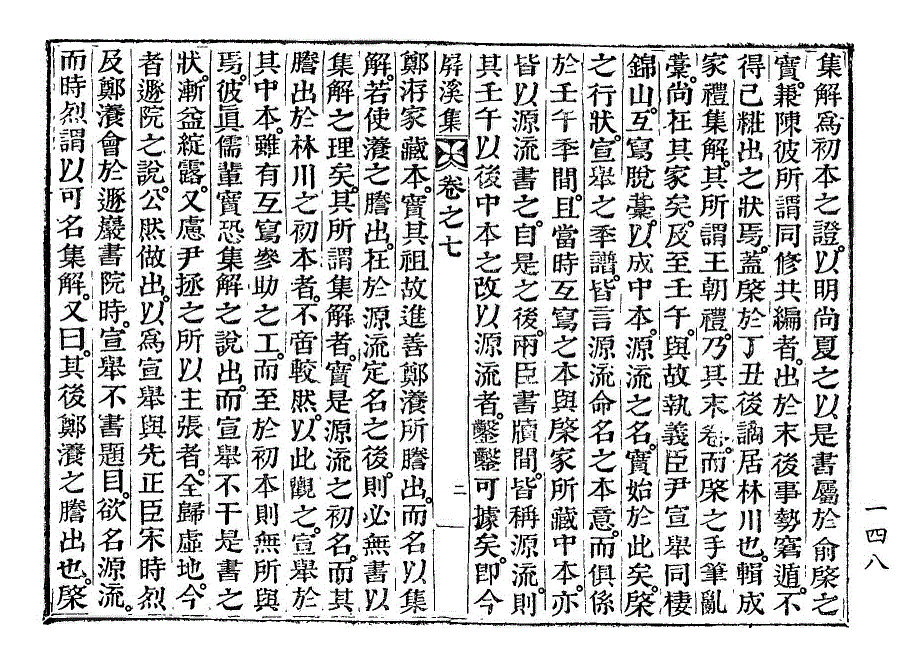 集解为初本之證。以明尚夏之以是书属于俞棨之实。兼陈彼所谓同修共编者。出于末后事势窘遁。不得已妆出之状焉。盖棨于丁丑后谪居林川也。辑成家礼集解。其所谓王朝礼。乃其末卷。而棨之手笔乱藁。尚在其家矣。及至壬午。与故执义臣尹宣举同栖锦山。互写脱藁。以成中本。源流之名。实始于此矣。棨之行状。宣举之年谱。皆言源流命名之本意。而俱系于壬午年间。且当时互写之本与棨家所藏中本。亦皆以源流书之。自是之后。两臣书牍间。皆称源流。则其壬午以后中本之改以源流者。凿凿可据矣。即今郑荐家藏本。实其祖故进善郑瀁所誊出。而名以集解。若使瀁之誊出。在于源流定名之后。则必无书以集解之理矣。其所谓集解者。实是源流之初名。而其誊出于林川之初本者。不啻较然。以此观之。宣举于其中本。虽有互写参助之工。而至于初本则无所与焉。彼真儒辈实恐集解之说出。而宣举不干是书之状。渐益绽露。又虑尹拯之所以主张者。全归虚地。今者遁院之说。公然做出。以为宣举与先正臣宋时烈及郑瀁会于遁岩书院时。宣举不书题目。欲名源流。而时烈谓以可名集解。又曰。其后郑瀁之誊出也。棨
集解为初本之證。以明尚夏之以是书属于俞棨之实。兼陈彼所谓同修共编者。出于末后事势窘遁。不得已妆出之状焉。盖棨于丁丑后谪居林川也。辑成家礼集解。其所谓王朝礼。乃其末卷。而棨之手笔乱藁。尚在其家矣。及至壬午。与故执义臣尹宣举同栖锦山。互写脱藁。以成中本。源流之名。实始于此矣。棨之行状。宣举之年谱。皆言源流命名之本意。而俱系于壬午年间。且当时互写之本与棨家所藏中本。亦皆以源流书之。自是之后。两臣书牍间。皆称源流。则其壬午以后中本之改以源流者。凿凿可据矣。即今郑荐家藏本。实其祖故进善郑瀁所誊出。而名以集解。若使瀁之誊出。在于源流定名之后。则必无书以集解之理矣。其所谓集解者。实是源流之初名。而其誊出于林川之初本者。不啻较然。以此观之。宣举于其中本。虽有互写参助之工。而至于初本则无所与焉。彼真儒辈实恐集解之说出。而宣举不干是书之状。渐益绽露。又虑尹拯之所以主张者。全归虚地。今者遁院之说。公然做出。以为宣举与先正臣宋时烈及郑瀁会于遁岩书院时。宣举不书题目。欲名源流。而时烈谓以可名集解。又曰。其后郑瀁之誊出也。棨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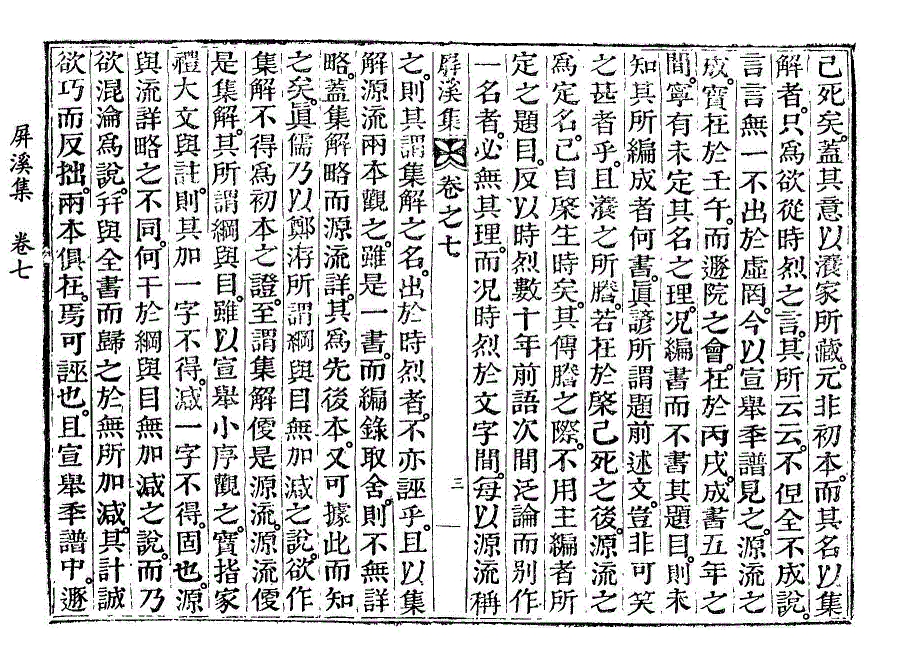 已死矣。盖其意以瀁家所藏。元非初本。而其名以集解者。只为欲从时烈之言。其所云云。不但全不成说。言言无一不出于虚罔。今以宣举年谱见之。源流之成。实在于壬午。而遁院之会。在于丙戌。成书五年之间。宁有未定其名之理。况编书而不书其题目。则未知其所编成者何书。真谚所谓题前述文。岂非可笑之甚者乎。且瀁之所誊。若在于棨已死之后。源流之为定名。已自棨生时矣。其传誊之际。不用主编者所定之题目。反以时烈数十年前语次间泛论而别作一名者。必无其理。而况时烈于文字间。每以源流称之。则其谓集解之名。出于时烈者。不亦诬乎。且以集解源流两本观之。虽是一书。而编录取舍。则不无详略。盖集解略而源流详。其为先后本。又可据此而知之矣。真儒乃以郑荐所谓纲与目无加减之说。欲作集解不得为初本之證。至谓集解便是源流。源流便是集解。其所谓纲与目。虽以宣举小序观之。实指家礼大文与注。则其加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固也。源与流详略之不同。何干于纲与目无加减之说。而乃欲混沦为说。并与全书而归之于无所加减。其计诚欲巧而反拙。两本俱在。焉可诬也。且宣举年谱中。遁
已死矣。盖其意以瀁家所藏。元非初本。而其名以集解者。只为欲从时烈之言。其所云云。不但全不成说。言言无一不出于虚罔。今以宣举年谱见之。源流之成。实在于壬午。而遁院之会。在于丙戌。成书五年之间。宁有未定其名之理。况编书而不书其题目。则未知其所编成者何书。真谚所谓题前述文。岂非可笑之甚者乎。且瀁之所誊。若在于棨已死之后。源流之为定名。已自棨生时矣。其传誊之际。不用主编者所定之题目。反以时烈数十年前语次间泛论而别作一名者。必无其理。而况时烈于文字间。每以源流称之。则其谓集解之名。出于时烈者。不亦诬乎。且以集解源流两本观之。虽是一书。而编录取舍。则不无详略。盖集解略而源流详。其为先后本。又可据此而知之矣。真儒乃以郑荐所谓纲与目无加减之说。欲作集解不得为初本之證。至谓集解便是源流。源流便是集解。其所谓纲与目。虽以宣举小序观之。实指家礼大文与注。则其加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固也。源与流详略之不同。何干于纲与目无加减之说。而乃欲混沦为说。并与全书而归之于无所加减。其计诚欲巧而反拙。两本俱在。焉可诬也。且宣举年谱中。遁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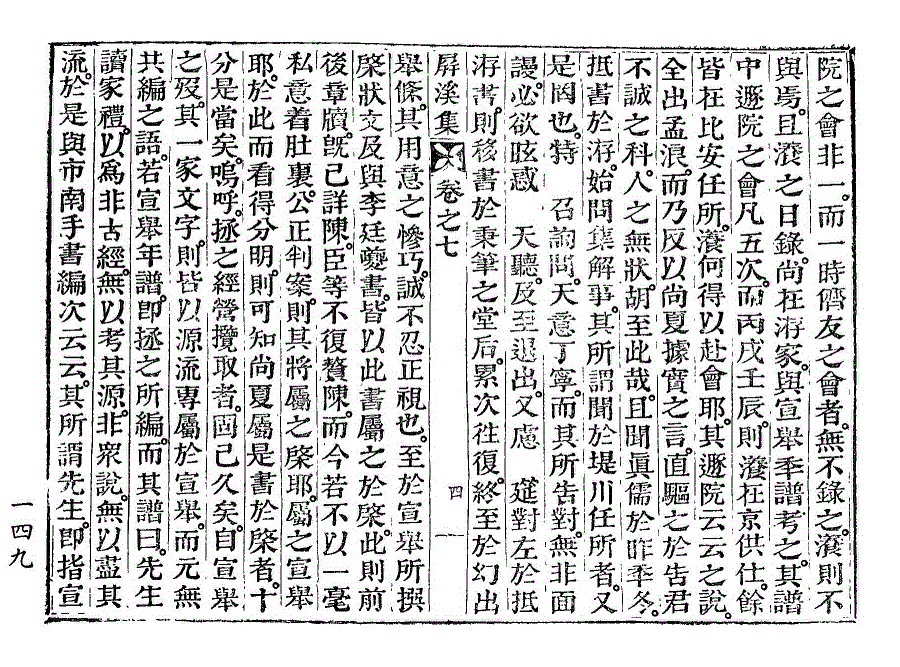 院之会非一。而一时侪友之会者。无不录之。瀁则不与焉。且瀁之日录。尚在荐家。与宣举年谱考之。其谱中遁院之会凡五次。而丙戌壬辰。则瀁在京供仕。馀皆在比安任所。瀁何得以赴会耶。其遁院云云之说。全出孟浪。而乃反以尚夏据实之言。直驱之于告君不诚之科。人之无状。胡至此哉。且闻真儒于昨年冬。抵书于荐。始问集解事。其所谓闻于堤川任所者。又是罔也。特 召询问。天意丁宁。而其所告对。无非面谩。必欲眩惑 天听。及至退出。又虑 筵对左于抵荐书。则移书于秉笔之堂后。累次往复。终至于幻出举条。其用意之惨巧。诚不忍正视也。至于宣举所撰棨状文及与李廷夔书。皆以此书属之于棨。此则前后章牍。既已详陈。臣等不复赘陈。而今若不以一毫私意着肚里。公正判案。则其将属之棨耶。属之宣举耶。于此而看得分明。则可知尚夏属是书于棨者。十分是当矣。呜呼。拯之经营揽取者。固已久矣。自宣举之殁。其一家文字。则皆以源流专属于宣举。而元无共编之语。若宣举年谱。即拯之所编。而其谱曰。先生读家礼。以为非古经。无以考其源。非众说。无以尽其流。于是与市南手书编次云云。其所谓先生。即指宣
院之会非一。而一时侪友之会者。无不录之。瀁则不与焉。且瀁之日录。尚在荐家。与宣举年谱考之。其谱中遁院之会凡五次。而丙戌壬辰。则瀁在京供仕。馀皆在比安任所。瀁何得以赴会耶。其遁院云云之说。全出孟浪。而乃反以尚夏据实之言。直驱之于告君不诚之科。人之无状。胡至此哉。且闻真儒于昨年冬。抵书于荐。始问集解事。其所谓闻于堤川任所者。又是罔也。特 召询问。天意丁宁。而其所告对。无非面谩。必欲眩惑 天听。及至退出。又虑 筵对左于抵荐书。则移书于秉笔之堂后。累次往复。终至于幻出举条。其用意之惨巧。诚不忍正视也。至于宣举所撰棨状文及与李廷夔书。皆以此书属之于棨。此则前后章牍。既已详陈。臣等不复赘陈。而今若不以一毫私意着肚里。公正判案。则其将属之棨耶。属之宣举耶。于此而看得分明。则可知尚夏属是书于棨者。十分是当矣。呜呼。拯之经营揽取者。固已久矣。自宣举之殁。其一家文字。则皆以源流专属于宣举。而元无共编之语。若宣举年谱。即拯之所编。而其谱曰。先生读家礼。以为非古经。无以考其源。非众说。无以尽其流。于是与市南手书编次云云。其所谓先生。即指宣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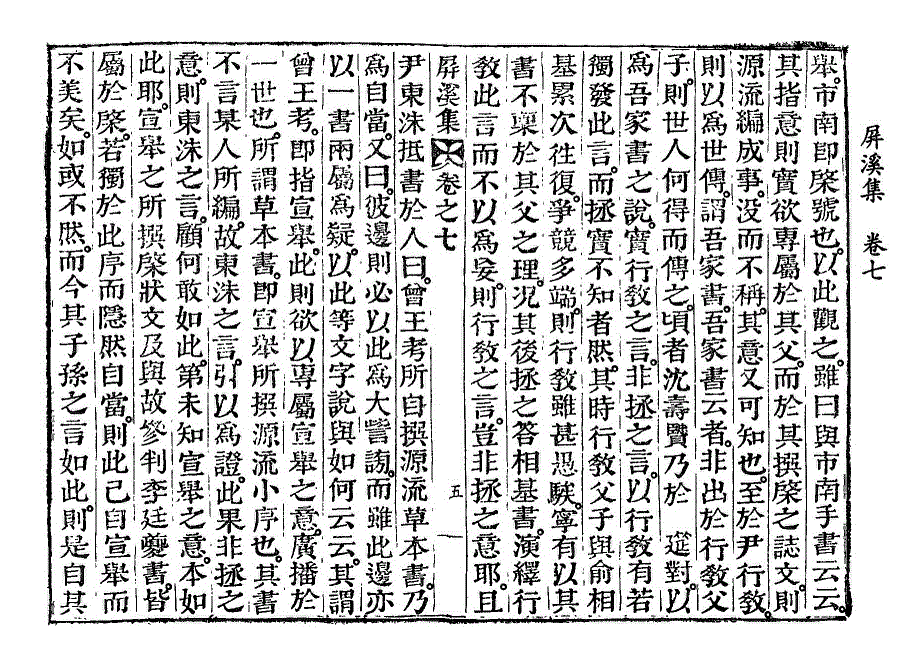 举。市南即棨号也。以此观之。虽曰与市南手书云云。其指意则实欲专属于其父。而于其撰棨之志文。则源流编成事。没而不称。其意又可知也。至于尹行教。则以为世传。谓吾家书。吾家书云者。非出于行教父子。则世人何得而传之。顷者沈寿贤乃于 筵对。以为吾家书之说。实行教之言。非拯之言。以行教有若独发此言。而拯实不知者然。其时行教父子与俞相基累次往复。争竞多端。则行教虽甚愚騃。宁有以其书不禀于其父之理。况其后拯之答相基书。演绎行教此言而不以为妄。则行教之言。岂非拯之意耶。且尹东洙抵书于人曰。曾王考所自撰源流草本书。乃为自当。又曰。彼边则必以此为大訾谤。而虽此边亦以一书两属为疑。以此等文字说与如何云云。其谓曾王考。即指宣举。此则欲以专属宣举之意。广播于一世也。所谓草本书。即宣举所撰源流小序也。其书不言某人所编。故东洙之言。引以为證。此果非拯之意。则东洙之言。顾何敢如此。第未知宣举之意。本如此耶。宣举之所撰棨状文及与故参判李廷夔书。皆属于棨。若独于此序而隐然自当。则此已自宣举而不美矣。如或不然。而今其子孙之言如此。则是自其
举。市南即棨号也。以此观之。虽曰与市南手书云云。其指意则实欲专属于其父。而于其撰棨之志文。则源流编成事。没而不称。其意又可知也。至于尹行教。则以为世传。谓吾家书。吾家书云者。非出于行教父子。则世人何得而传之。顷者沈寿贤乃于 筵对。以为吾家书之说。实行教之言。非拯之言。以行教有若独发此言。而拯实不知者然。其时行教父子与俞相基累次往复。争竞多端。则行教虽甚愚騃。宁有以其书不禀于其父之理。况其后拯之答相基书。演绎行教此言而不以为妄。则行教之言。岂非拯之意耶。且尹东洙抵书于人曰。曾王考所自撰源流草本书。乃为自当。又曰。彼边则必以此为大訾谤。而虽此边亦以一书两属为疑。以此等文字说与如何云云。其谓曾王考。即指宣举。此则欲以专属宣举之意。广播于一世也。所谓草本书。即宣举所撰源流小序也。其书不言某人所编。故东洙之言。引以为證。此果非拯之意。则东洙之言。顾何敢如此。第未知宣举之意。本如此耶。宣举之所撰棨状文及与故参判李廷夔书。皆属于棨。若独于此序而隐然自当。则此已自宣举而不美矣。如或不然。而今其子孙之言如此。则是自其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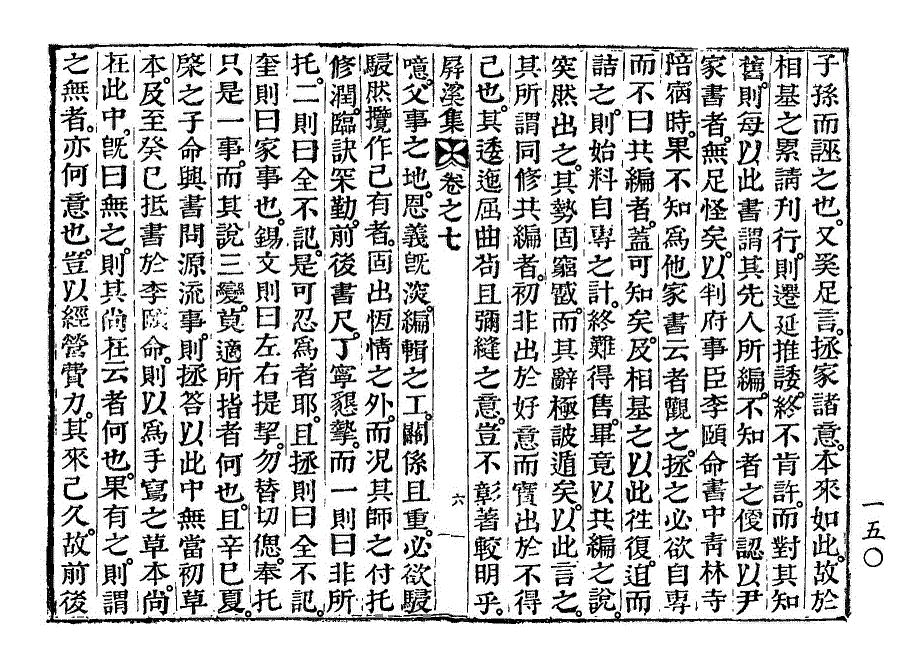 子孙而诬之也。又奚足言。拯家诸意。本来如此。故于相基之累请刊行。则迁延推诿。终不肯许。而对其知旧。则每以此书谓其先人所编。不知者之便认以尹家书者。无足怪矣。以判府事臣李颐命书中青林寺陪宿时。果不知为他家书云者观之。拯之必欲自专而不曰共编者。盖可知矣。及相基之以此往复。迫而诘之。则始料自专之计。终难得售。毕竟以共编之说。突然出之。其势固穷蹙。而其辞极诐遁矣。以此言之。其所谓同修共编者。初非出于好意而实出于不得已也。其逶迤屈曲苟且弥缝之意。岂不彰著较明乎。噫。父事之地。恩义既深。编辑之工。关系且重。必欲骎骎然揽作己有者。固出恒情之外。而况其师之付托修润。临诀深勤。前后书尺。丁宁恳挚。而一则曰非所托。二则曰全不记。是可忍为者耶。且拯则曰全不记。奎则曰家事也。锡文则曰左右提挈。勿替切偲。奉托只是一事。而其说三变。莫适所指者何也。且辛巳夏。棨之子命兴书问源流事。则拯答以此中无当初草本。及至癸巳抵书于李颐命。则以为手写之草本。尚在此中。既曰无之。则其尚在云者何也。果有之。则谓之无者。亦何意也。岂以经营费力。其来已久。故前后
子孙而诬之也。又奚足言。拯家诸意。本来如此。故于相基之累请刊行。则迁延推诿。终不肯许。而对其知旧。则每以此书谓其先人所编。不知者之便认以尹家书者。无足怪矣。以判府事臣李颐命书中青林寺陪宿时。果不知为他家书云者观之。拯之必欲自专而不曰共编者。盖可知矣。及相基之以此往复。迫而诘之。则始料自专之计。终难得售。毕竟以共编之说。突然出之。其势固穷蹙。而其辞极诐遁矣。以此言之。其所谓同修共编者。初非出于好意而实出于不得已也。其逶迤屈曲苟且弥缝之意。岂不彰著较明乎。噫。父事之地。恩义既深。编辑之工。关系且重。必欲骎骎然揽作己有者。固出恒情之外。而况其师之付托修润。临诀深勤。前后书尺。丁宁恳挚。而一则曰非所托。二则曰全不记。是可忍为者耶。且拯则曰全不记。奎则曰家事也。锡文则曰左右提挈。勿替切偲。奉托只是一事。而其说三变。莫适所指者何也。且辛巳夏。棨之子命兴书问源流事。则拯答以此中无当初草本。及至癸巳抵书于李颐命。则以为手写之草本。尚在此中。既曰无之。则其尚在云者何也。果有之。则谓之无者。亦何意也。岂以经营费力。其来已久。故前后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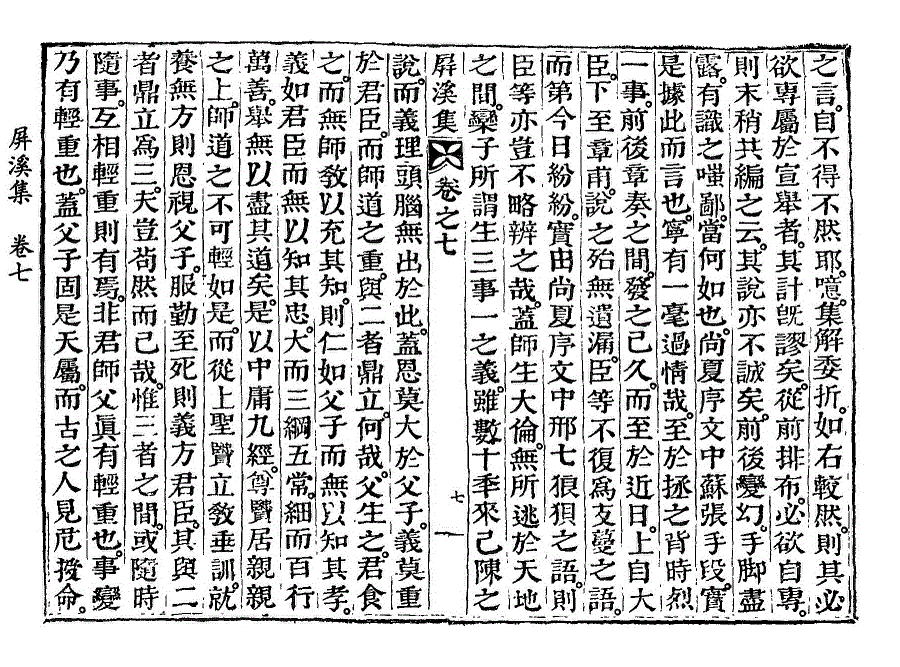 之言。自不得不然耶。噫。集解委折。如右较然。则其必欲专属于宣举者。其计既谬矣。从前排布。必欲自专。则末稍共编之云。其说亦不诚矣。前后变幻。手脚尽露。有识之嗤鄙。当何如也。尚夏序文中苏张手段。实是据此而言也。宁有一毫过情哉。至于拯之背时烈一事。前后章奏之间。发之已久。而至于近日。上自大臣。下至章甫。说之殆无遗漏。臣等不复为支蔓之语。而第今日纷纷。实由尚夏序文中邢七狼狈之语。则臣等亦岂不略辨之哉。盖师生大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栾子所谓生三事一之义。虽数十年来已陈之说。而义理头脑无出于此。盖恩莫大于父子。义莫重于君臣。而师道之重。与二者鼎立。何哉。父生之。君食之。而无师教以充其知。则仁如父子而无以知其孝。义如君臣而无以知其忠。大而三纲五常。细而百行万善。举无以尽其道矣。是以中庸九经。尊贤居亲亲之上。师道之不可轻如是。而从上圣贤立教垂训。就养无方则恩视父子。服勤至死则义方君臣。其与二者鼎立为三。夫岂苟然而已哉。惟三者之间。或随时随事。互相轻重则有焉。非君师父真有轻重也。事变乃有轻重也。盖父子固是天属。而古之人见危授命。
之言。自不得不然耶。噫。集解委折。如右较然。则其必欲专属于宣举者。其计既谬矣。从前排布。必欲自专。则末稍共编之云。其说亦不诚矣。前后变幻。手脚尽露。有识之嗤鄙。当何如也。尚夏序文中苏张手段。实是据此而言也。宁有一毫过情哉。至于拯之背时烈一事。前后章奏之间。发之已久。而至于近日。上自大臣。下至章甫。说之殆无遗漏。臣等不复为支蔓之语。而第今日纷纷。实由尚夏序文中邢七狼狈之语。则臣等亦岂不略辨之哉。盖师生大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栾子所谓生三事一之义。虽数十年来已陈之说。而义理头脑无出于此。盖恩莫大于父子。义莫重于君臣。而师道之重。与二者鼎立。何哉。父生之。君食之。而无师教以充其知。则仁如父子而无以知其孝。义如君臣而无以知其忠。大而三纲五常。细而百行万善。举无以尽其道矣。是以中庸九经。尊贤居亲亲之上。师道之不可轻如是。而从上圣贤立教垂训。就养无方则恩视父子。服勤至死则义方君臣。其与二者鼎立为三。夫岂苟然而已哉。惟三者之间。或随时随事。互相轻重则有焉。非君师父真有轻重也。事变乃有轻重也。盖父子固是天属。而古之人见危授命。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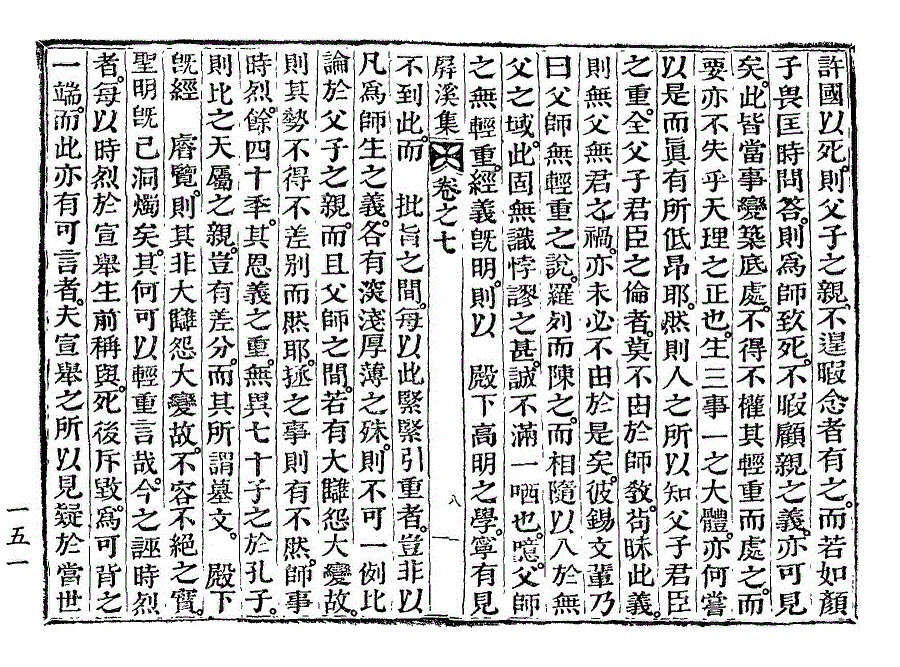 许国以死。则父子之亲。不遑暇念者有之。而若如颜子畏匡时问答。则为师致死。不暇顾亲之义。亦可见矣。此皆当事变筑底处。不得不权其轻重而处之。而要亦不失乎天理之正也。生三事一之大体。亦何尝以是而真有所低昂耶。然则人之所以知父子君臣之重。全父子君臣之伦者。莫不由于师教。苟昧此义。则无父无君之祸。亦未必不由于是矣。彼锡文辈乃曰父师无轻重之说。罗列而陈之。而相随以入于无父之域。此固无识悖谬之甚。诚不满一哂也。噫。父师之无轻重。经义既明。则以 殿下高明之学。宁有见不到此。而 批旨之间。每以此紧紧引重者。岂非以凡为师生之义。各有深浅厚薄之殊。则不可一例比论于父子之亲。而且父师之间。若有大雠怨大变故。则其势不得不差别而然耶。拯之事则有不然。师事时烈。馀四十年。其恩义之重。无异七十子之于孔子。则比之天属之亲。岂有差分。而其所谓墓文。 殿下既经 睿览。则其非大雠怨大变故。不容不绝之实。圣明既已洞烛矣。其何可以轻重言哉。今之诬时烈者。每以时烈于宣举生前称与。死后斥毁。为可背之一端。而此亦有可言者。夫宣举之所以见疑于当世
许国以死。则父子之亲。不遑暇念者有之。而若如颜子畏匡时问答。则为师致死。不暇顾亲之义。亦可见矣。此皆当事变筑底处。不得不权其轻重而处之。而要亦不失乎天理之正也。生三事一之大体。亦何尝以是而真有所低昂耶。然则人之所以知父子君臣之重。全父子君臣之伦者。莫不由于师教。苟昧此义。则无父无君之祸。亦未必不由于是矣。彼锡文辈乃曰父师无轻重之说。罗列而陈之。而相随以入于无父之域。此固无识悖谬之甚。诚不满一哂也。噫。父师之无轻重。经义既明。则以 殿下高明之学。宁有见不到此。而 批旨之间。每以此紧紧引重者。岂非以凡为师生之义。各有深浅厚薄之殊。则不可一例比论于父子之亲。而且父师之间。若有大雠怨大变故。则其势不得不差别而然耶。拯之事则有不然。师事时烈。馀四十年。其恩义之重。无异七十子之于孔子。则比之天属之亲。岂有差分。而其所谓墓文。 殿下既经 睿览。则其非大雠怨大变故。不容不绝之实。圣明既已洞烛矣。其何可以轻重言哉。今之诬时烈者。每以时烈于宣举生前称与。死后斥毁。为可背之一端。而此亦有可言者。夫宣举之所以见疑于当世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2H 页
 者。唯有两事。偷生与党恶也。所以取重于君子者。亦有两事。悔过与绝鑴也。方其偷生也。人固耻之。而及其悔过则贤而取之。方其党恶也。人固恶之。而及其绝鑴则进而与之。夫人之心。岂有他哉。不过善善而恶恶焉耳。及宣举殁而拯受贼鑴酹文。不讳其平日相与之笃然后。其父党恶之迹彰。而绝鑴之言虚矣。至引其父疏语。以明其自废之不由于江都事然后。其父偷生之实著。而悔过之说诬矣。此拯之两世本末。只如斯而已。而时烈所以处宣举之前后有异者。亦由其父子之处义前后不同故也。其所以善善焉恶恶焉者。莫非一公案打出。则此岂可为背时烈之端耶。噫。设令拯之背时烈。出于为其父之意。既无可背之端。则尚难免犯分之罪。况其心不专在此而自有所计较者耶。呜呼。拯之家法。多在利害。士类之窃议久矣。时烈尝以贼鑴为斯文乱贼。而为鑴党所仇疾。故已自宣举在时。反以世祸目之。及至癸丑。奸党窥觊。时事将倾。则拯乃以其父己酉拟与时烈书。始视时烈。其书即劝用贼鑴者。而撰其父年谱也。又极意赞鑴。时烈于是固疑其心矣。鑴既得志。士祸滔天。时烈首被毒镝。北窜南迁。而拯于是时。乃拜亚宪。既
者。唯有两事。偷生与党恶也。所以取重于君子者。亦有两事。悔过与绝鑴也。方其偷生也。人固耻之。而及其悔过则贤而取之。方其党恶也。人固恶之。而及其绝鑴则进而与之。夫人之心。岂有他哉。不过善善而恶恶焉耳。及宣举殁而拯受贼鑴酹文。不讳其平日相与之笃然后。其父党恶之迹彰。而绝鑴之言虚矣。至引其父疏语。以明其自废之不由于江都事然后。其父偷生之实著。而悔过之说诬矣。此拯之两世本末。只如斯而已。而时烈所以处宣举之前后有异者。亦由其父子之处义前后不同故也。其所以善善焉恶恶焉者。莫非一公案打出。则此岂可为背时烈之端耶。噫。设令拯之背时烈。出于为其父之意。既无可背之端。则尚难免犯分之罪。况其心不专在此而自有所计较者耶。呜呼。拯之家法。多在利害。士类之窃议久矣。时烈尝以贼鑴为斯文乱贼。而为鑴党所仇疾。故已自宣举在时。反以世祸目之。及至癸丑。奸党窥觊。时事将倾。则拯乃以其父己酉拟与时烈书。始视时烈。其书即劝用贼鑴者。而撰其父年谱也。又极意赞鑴。时烈于是固疑其心矣。鑴既得志。士祸滔天。时烈首被毒镝。北窜南迁。而拯于是时。乃拜亚宪。既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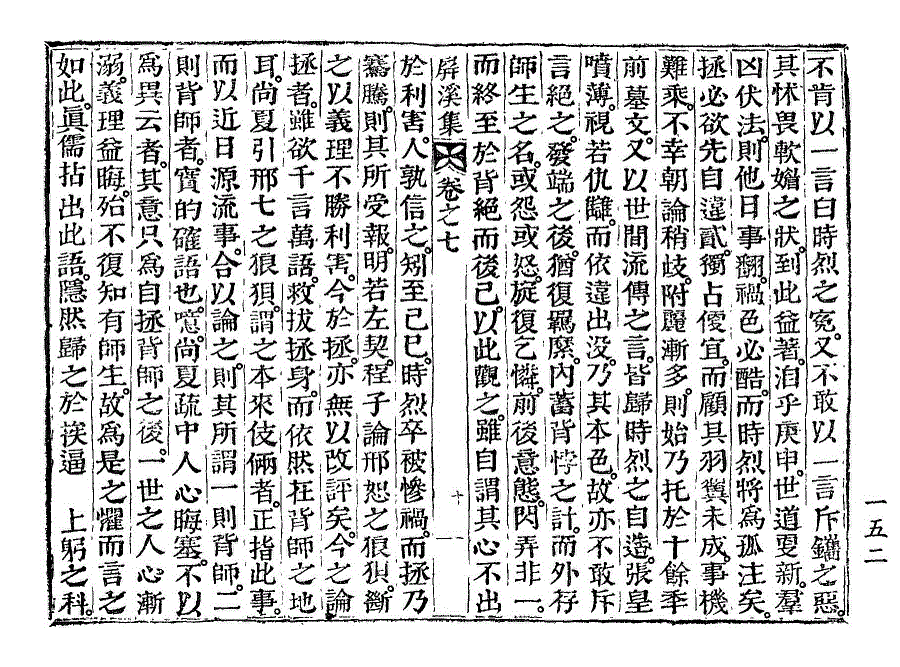 不肯以一言白时烈之冤。又不敢以一言斥鑴之恶。其怵畏软媚之状。到此益著。洎乎庚申。世道更新。群凶伏法。则他日事翻。祸色必酷。而时烈将为孤注矣。拯必欲先自违贰。独占便宜。而顾其羽翼未成。事机难乘。不幸朝论稍歧。附丽渐多。则始乃托于十馀年前墓文。又以世间流传之言。皆归时烈之自造。张皇喷薄。视若仇雠。而依违出没。乃其本色。故亦不敢斥言绝之。发端之后。犹复羁縻。内蓄背悖之计。而外存师生之名。或怨或怒。旋复乞怜。前后意态。闪弄非一。而终至于背绝而后已。以此观之。虽自谓其心不出于利害。人孰信之。矧至己巳。时烈卒被惨祸。而拯乃骞腾。则其所受报。明若左契。程子论邢恕之狼狈。断之以义理不胜利害。今于拯。亦无以改评矣。今之论拯者。虽欲千言万语。救拔拯身。而依然在背师之地耳。尚夏引邢七之狼狈。谓之本来伎俩者。正指此事。而以近日源流事。合以论之。则其所谓一则背师。二则背师者。实的确语也。噫。尚夏疏中人心晦塞。不以为异云者。其意只为自拯背师之后。一世之人心渐溺。义理益晦。殆不复知有师生。故为是之惧而言之如此。真儒拈出此语。隐然归之于挨逼 上躬之科。
不肯以一言白时烈之冤。又不敢以一言斥鑴之恶。其怵畏软媚之状。到此益著。洎乎庚申。世道更新。群凶伏法。则他日事翻。祸色必酷。而时烈将为孤注矣。拯必欲先自违贰。独占便宜。而顾其羽翼未成。事机难乘。不幸朝论稍歧。附丽渐多。则始乃托于十馀年前墓文。又以世间流传之言。皆归时烈之自造。张皇喷薄。视若仇雠。而依违出没。乃其本色。故亦不敢斥言绝之。发端之后。犹复羁縻。内蓄背悖之计。而外存师生之名。或怨或怒。旋复乞怜。前后意态。闪弄非一。而终至于背绝而后已。以此观之。虽自谓其心不出于利害。人孰信之。矧至己巳。时烈卒被惨祸。而拯乃骞腾。则其所受报。明若左契。程子论邢恕之狼狈。断之以义理不胜利害。今于拯。亦无以改评矣。今之论拯者。虽欲千言万语。救拔拯身。而依然在背师之地耳。尚夏引邢七之狼狈。谓之本来伎俩者。正指此事。而以近日源流事。合以论之。则其所谓一则背师。二则背师者。实的确语也。噫。尚夏疏中人心晦塞。不以为异云者。其意只为自拯背师之后。一世之人心渐溺。义理益晦。殆不复知有师生。故为是之惧而言之如此。真儒拈出此语。隐然归之于挨逼 上躬之科。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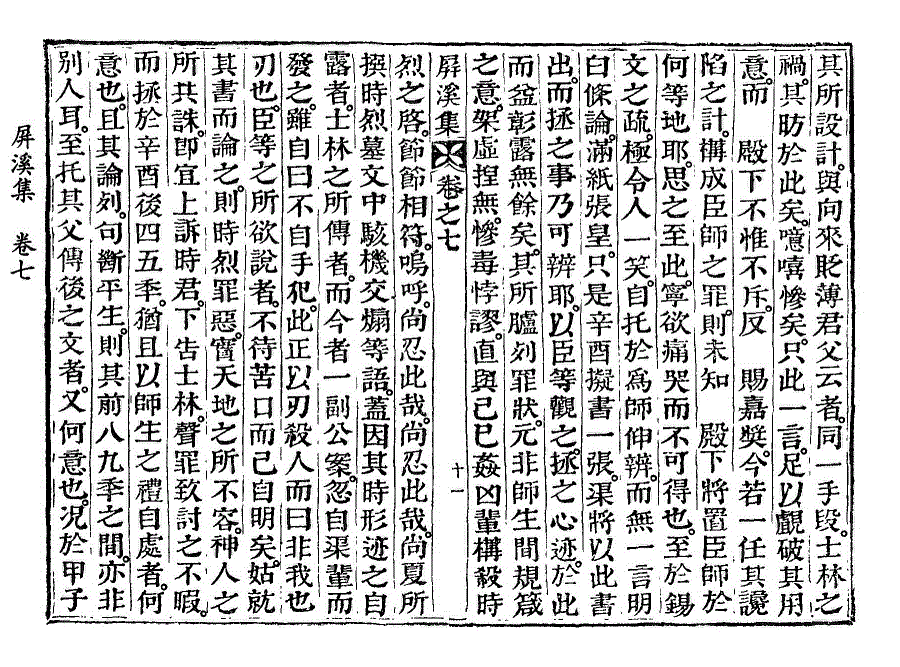 其所设计。与向来贬薄君父云者。同一手段。士林之祸。其昉于此矣。噫嘻惨矣。只此一言。足以觑破其用意。而 殿下不惟不斥。反 赐嘉奖。今若一任其谗陷之计。构成臣师之罪。则未知 殿下将置臣师于何等地耶。思之至此。宁欲痛哭而不可得也。至于锡文之疏。极令人一笑。自托于为师伸辨。而无一言明白条论。满纸张皇。只是辛酉拟书一张。渠将以此书出。而拯之事乃可辨耶。以臣等观之。拯之心迹。于此而益彰露无馀矣。其所胪列罪状。元非师生间规箴之意。架虚捏无。惨毒悖谬。直与己巳奸凶辈构杀时烈之启。节节相符。呜呼。尚忍此哉。尚忍此哉。尚夏所撰时烈墓文中骇机交煽等语。盖因其时形迹之自露者。士林之所传者。而今者一副公案。忽自渠辈而发之。虽自曰不自手犯。此正以刃杀人而曰非我也刃也。臣等之所欲说者。不待苦口而已自明矣。姑就其书而论之。则时烈罪恶。实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诛。即宜上诉时君。下告士林。声罪致讨之不暇。而拯于辛酉后四五年。犹且以师生之礼自处者。何意也。且其论列。句断平生。则其前八九年之间。亦非别人耳。至托其父传后之文者。又何意也。况于甲子
其所设计。与向来贬薄君父云者。同一手段。士林之祸。其昉于此矣。噫嘻惨矣。只此一言。足以觑破其用意。而 殿下不惟不斥。反 赐嘉奖。今若一任其谗陷之计。构成臣师之罪。则未知 殿下将置臣师于何等地耶。思之至此。宁欲痛哭而不可得也。至于锡文之疏。极令人一笑。自托于为师伸辨。而无一言明白条论。满纸张皇。只是辛酉拟书一张。渠将以此书出。而拯之事乃可辨耶。以臣等观之。拯之心迹。于此而益彰露无馀矣。其所胪列罪状。元非师生间规箴之意。架虚捏无。惨毒悖谬。直与己巳奸凶辈构杀时烈之启。节节相符。呜呼。尚忍此哉。尚忍此哉。尚夏所撰时烈墓文中骇机交煽等语。盖因其时形迹之自露者。士林之所传者。而今者一副公案。忽自渠辈而发之。虽自曰不自手犯。此正以刃杀人而曰非我也刃也。臣等之所欲说者。不待苦口而已自明矣。姑就其书而论之。则时烈罪恶。实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诛。即宜上诉时君。下告士林。声罪致讨之不暇。而拯于辛酉后四五年。犹且以师生之礼自处者。何意也。且其论列。句断平生。则其前八九年之间。亦非别人耳。至托其父传后之文者。又何意也。况于甲子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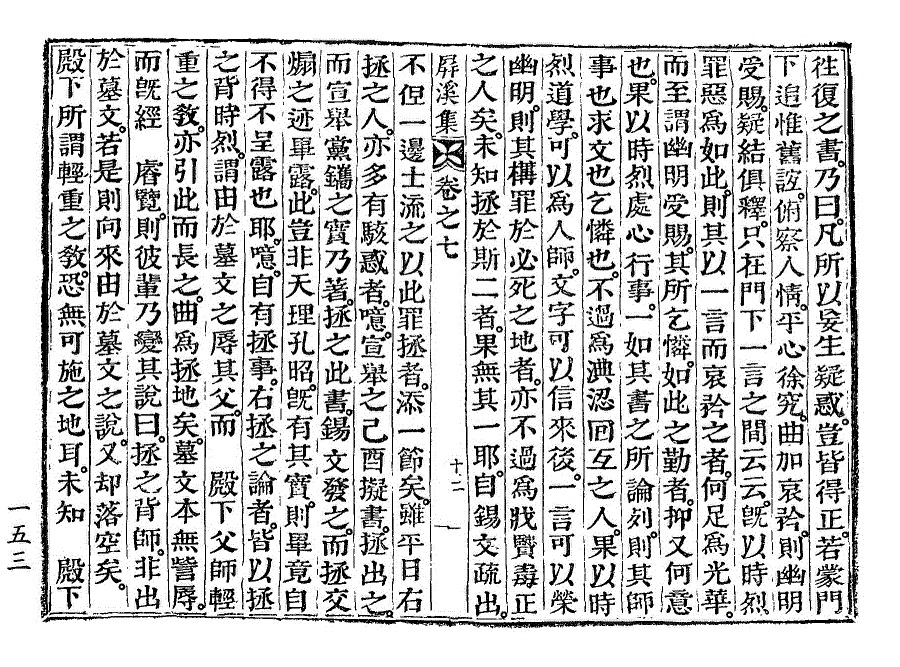 往复之书。乃曰。凡所以妄生疑惑。岂皆得正。若蒙门下追惟旧谊。俯察人情。平心徐究。曲加哀矜。则幽明受赐。疑结俱释。只在门下一言之间云云。既以时烈罪恶为如此。则其以一言而哀矜之者。何足为光华。而至谓幽明受赐。其所乞怜。如此之勤者。抑又何意也。果以时烈处心行事。一如其书之所论列。则其师事也求文也乞怜也。不过为淟涊回互之人。果以时烈道学。可以为人师。文字可以信来后。一言可以荣幽明。则其构罪于必死之地者。亦不过为戕贤毒正之人矣。未知拯于斯二者。果无其一耶。自锡文疏出。不但一边士流之以此罪拯者。添一节矣。虽平日右拯之人。亦多有骇惑者。噫。宣举之己酉拟书。拯出之。而宣举党鑴之实乃著。拯之此书。锡文发之。而拯交煽之迹毕露。此岂非天理孔昭。既有其实。则毕竟自不得不呈露也耶。噫。自有拯事。右拯之论者。皆以拯之背时烈。谓由于墓文之辱其父。而 殿下父师轻重之教。亦引此而长之。曲为拯地矣。墓文本无訾辱。而既经 睿览。则彼辈乃变其说曰。拯之背师。非出于墓文。若是则向来由于墓文之说。又却落空矣。 殿下所谓轻重之教。恐无可施之地耳。未知 殿下
往复之书。乃曰。凡所以妄生疑惑。岂皆得正。若蒙门下追惟旧谊。俯察人情。平心徐究。曲加哀矜。则幽明受赐。疑结俱释。只在门下一言之间云云。既以时烈罪恶为如此。则其以一言而哀矜之者。何足为光华。而至谓幽明受赐。其所乞怜。如此之勤者。抑又何意也。果以时烈处心行事。一如其书之所论列。则其师事也求文也乞怜也。不过为淟涊回互之人。果以时烈道学。可以为人师。文字可以信来后。一言可以荣幽明。则其构罪于必死之地者。亦不过为戕贤毒正之人矣。未知拯于斯二者。果无其一耶。自锡文疏出。不但一边士流之以此罪拯者。添一节矣。虽平日右拯之人。亦多有骇惑者。噫。宣举之己酉拟书。拯出之。而宣举党鑴之实乃著。拯之此书。锡文发之。而拯交煽之迹毕露。此岂非天理孔昭。既有其实。则毕竟自不得不呈露也耶。噫。自有拯事。右拯之论者。皆以拯之背时烈。谓由于墓文之辱其父。而 殿下父师轻重之教。亦引此而长之。曲为拯地矣。墓文本无訾辱。而既经 睿览。则彼辈乃变其说曰。拯之背师。非出于墓文。若是则向来由于墓文之说。又却落空矣。 殿下所谓轻重之教。恐无可施之地耳。未知 殿下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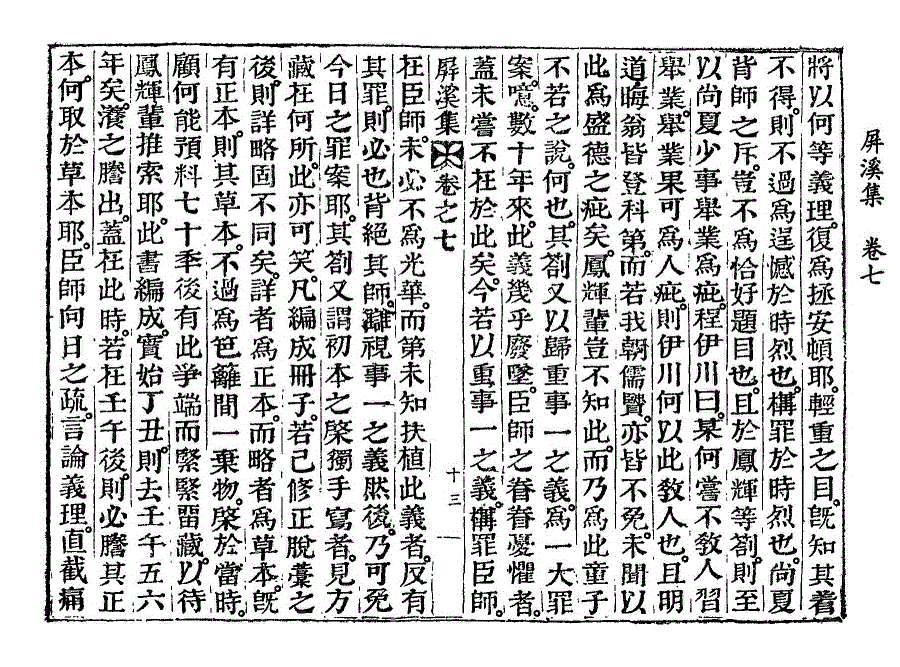 将以何等义理。复为拯安顿耶。轻重之目。既知其着不得。则不过为逞憾于时烈也。构罪于时烈也。尚夏背师之斥。岂不为恰好题目也。且于凤辉等劄。则至以尚夏少事举业为疵。程伊川曰。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举业果可为人疵。则伊川何以此教人也。且明道,晦翁皆登科第。而若我朝儒贤。亦皆不免。未闻以此为盛德之疵矣。凤辉辈岂不知此。而乃为此童子不若之说。何也。其劄又以归重事一之义。为一大罪案。噫。数十年来。此义几乎废坠。臣师之眷眷忧惧者。盖未尝不在于此矣。今若以重事一之义。构罪臣师。在臣师。未必不为光华。而第未知扶植此义者。反有其罪。则必也背绝其师。雠视事一之义然后。乃可免今日之罪案耶。其劄又谓初本之棨独手写者。见方藏在何所。此亦可笑。凡编成册子。若已修正脱藁之后。则详略固不同矣。详者为正本。而略者为草本。既有正本。则其草本。不过为笆篱间一弃物。棨于当时。顾何能预料七十年后有此争端而紧紧留藏。以待凤辉辈推索耶。此书编成。实始丁丑。则去壬午五六年矣。瀁之誊出。盖在此时。若在壬午后。则必誊其正本。何取于草本耶。臣师向日之疏。言论义理。直截痛
将以何等义理。复为拯安顿耶。轻重之目。既知其着不得。则不过为逞憾于时烈也。构罪于时烈也。尚夏背师之斥。岂不为恰好题目也。且于凤辉等劄。则至以尚夏少事举业为疵。程伊川曰。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举业果可为人疵。则伊川何以此教人也。且明道,晦翁皆登科第。而若我朝儒贤。亦皆不免。未闻以此为盛德之疵矣。凤辉辈岂不知此。而乃为此童子不若之说。何也。其劄又以归重事一之义。为一大罪案。噫。数十年来。此义几乎废坠。臣师之眷眷忧惧者。盖未尝不在于此矣。今若以重事一之义。构罪臣师。在臣师。未必不为光华。而第未知扶植此义者。反有其罪。则必也背绝其师。雠视事一之义然后。乃可免今日之罪案耶。其劄又谓初本之棨独手写者。见方藏在何所。此亦可笑。凡编成册子。若已修正脱藁之后。则详略固不同矣。详者为正本。而略者为草本。既有正本。则其草本。不过为笆篱间一弃物。棨于当时。顾何能预料七十年后有此争端而紧紧留藏。以待凤辉辈推索耶。此书编成。实始丁丑。则去壬午五六年矣。瀁之誊出。盖在此时。若在壬午后。则必誊其正本。何取于草本耶。臣师向日之疏。言论义理。直截痛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4L 页
 快。正如水临万仞。无少屈曲。有何密设圈套。有何关键甚密耶。且如滥致吹嘘等丑悖之说。只欲以恶言相加。全无伦理。辨之污口。臣等诚欲无言也。呜呼。尚夏所以论拯者。固以明伦理之重。劈邪正之分。而有辞于天下。不易于来后者。特以忤彼辈之所尊。犯 殿下之所忌。故特怒转沸。火色渐加。内而燬书之惨。斯已极矣。外而罢职之谴。更无顾惜。是何 殿下之明。乃为此举措也。噫。其书虽可火而其道不可火矣。其人虽可罪而其义不可灭矣。此于尚夏。何所损益。殿下所以湮绝其源。摧阏其道者。已至此极。臣等之结轖冤痛。岂但为世道之变。斯文之厄而已哉。噫。朱子有言曰。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应万事。直而已。此盖孔子所谓人生也直。孟子所谓以直养之意。而固先圣心授法门也。时烈之一动一静。一言一默。莫不遵用朱子。故一生所秉执以死生者。顾一直字耳。于其临诀。亦以此意眷眷传授于尚夏。而尚夏奉持此义。实有以身殉之意。今若气势所压。媕娿苟且。使斯道不复明于今与后。则师生付托之意。果安在哉。今日之破败。未必非一直字为之祟耳。然臣师之所担负。即时烈之道。时烈之道。即朱子之道。而孔孟以下
快。正如水临万仞。无少屈曲。有何密设圈套。有何关键甚密耶。且如滥致吹嘘等丑悖之说。只欲以恶言相加。全无伦理。辨之污口。臣等诚欲无言也。呜呼。尚夏所以论拯者。固以明伦理之重。劈邪正之分。而有辞于天下。不易于来后者。特以忤彼辈之所尊。犯 殿下之所忌。故特怒转沸。火色渐加。内而燬书之惨。斯已极矣。外而罢职之谴。更无顾惜。是何 殿下之明。乃为此举措也。噫。其书虽可火而其道不可火矣。其人虽可罪而其义不可灭矣。此于尚夏。何所损益。殿下所以湮绝其源。摧阏其道者。已至此极。臣等之结轖冤痛。岂但为世道之变。斯文之厄而已哉。噫。朱子有言曰。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应万事。直而已。此盖孔子所谓人生也直。孟子所谓以直养之意。而固先圣心授法门也。时烈之一动一静。一言一默。莫不遵用朱子。故一生所秉执以死生者。顾一直字耳。于其临诀。亦以此意眷眷传授于尚夏。而尚夏奉持此义。实有以身殉之意。今若气势所压。媕娿苟且。使斯道不复明于今与后。则师生付托之意。果安在哉。今日之破败。未必非一直字为之祟耳。然臣师之所担负。即时烈之道。时烈之道。即朱子之道。而孔孟以下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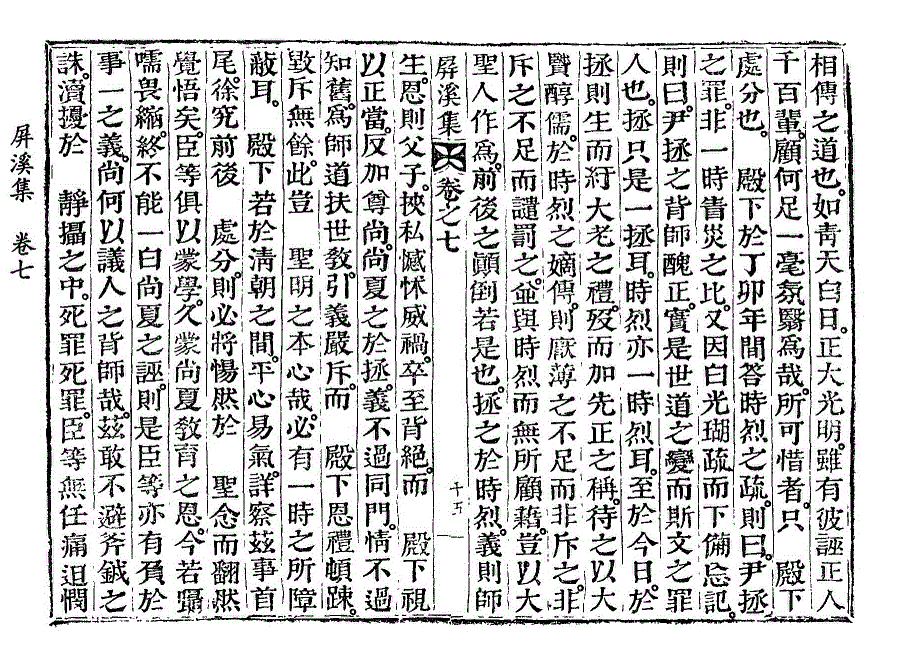 相传之道也。如青天白日。正大光明。虽有彼诬正人千百辈。顾何足一毫氛翳为哉。所可惜者。只 殿下处分也。 殿下于丁卯年间答时烈之疏。则曰。尹拯之罪。非一时眚灾之比。又因白光瑚疏而下备忘记。则曰。尹拯之背师丑正。实是世道之变而斯文之罪人也。拯只是一拯耳。时烈亦一时烈耳。至于今日。于拯则生而纡大老之礼。殁而加先正之称。待之以大贤醇儒。于时烈之嫡传。则厌薄之不足而非斥之。非斥之不足而谴罚之。并与时烈而无所顾藉。岂以大圣人作为。前后之颠倒若是也。拯之于时烈。义则师生。恩则父子。挟私憾怵威祸。卒至背绝。而 殿下视以正当。反加尊尚。尚夏之于拯。义不过同门。情不过知旧。为师道扶世教。引义严斥。而 殿下恩礼顿疏。毁斥无馀。此岂 圣明之本心哉。必有一时之所障蔽耳。 殿下若于清朝之间。平心易气。详察兹事首尾。徐究前后 处分。则必将惕然于 圣念而翻然觉悟矣。臣等俱以蒙学。久蒙尚夏教育之恩。今若嗫嚅畏缩。终不能一白尚夏之诬。则是臣等亦有负于事一之义。尚何以议人之背师哉。兹敢不避斧钺之诛。渎扰于 静摄之中。死罪死罪。臣等无任痛迫悯
相传之道也。如青天白日。正大光明。虽有彼诬正人千百辈。顾何足一毫氛翳为哉。所可惜者。只 殿下处分也。 殿下于丁卯年间答时烈之疏。则曰。尹拯之罪。非一时眚灾之比。又因白光瑚疏而下备忘记。则曰。尹拯之背师丑正。实是世道之变而斯文之罪人也。拯只是一拯耳。时烈亦一时烈耳。至于今日。于拯则生而纡大老之礼。殁而加先正之称。待之以大贤醇儒。于时烈之嫡传。则厌薄之不足而非斥之。非斥之不足而谴罚之。并与时烈而无所顾藉。岂以大圣人作为。前后之颠倒若是也。拯之于时烈。义则师生。恩则父子。挟私憾怵威祸。卒至背绝。而 殿下视以正当。反加尊尚。尚夏之于拯。义不过同门。情不过知旧。为师道扶世教。引义严斥。而 殿下恩礼顿疏。毁斥无馀。此岂 圣明之本心哉。必有一时之所障蔽耳。 殿下若于清朝之间。平心易气。详察兹事首尾。徐究前后 处分。则必将惕然于 圣念而翻然觉悟矣。臣等俱以蒙学。久蒙尚夏教育之恩。今若嗫嚅畏缩。终不能一白尚夏之诬。则是臣等亦有负于事一之义。尚何以议人之背师哉。兹敢不避斧钺之诛。渎扰于 静摄之中。死罪死罪。臣等无任痛迫悯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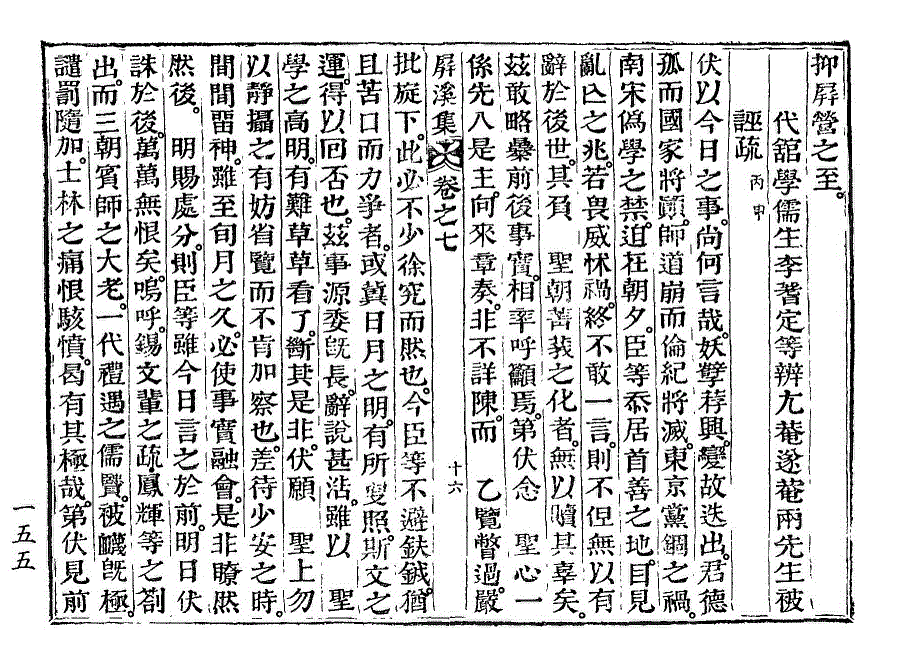 抑屏营之至。
抑屏营之至。代馆学儒生李蓍定等辨尤庵遂庵两先生被诬疏(丙申)
伏以今日之事。尚何言哉。妖孽荐兴。变故迭出。君德孤而国家将颠。师道崩而伦纪将灭。东京党锢之祸。南宋伪学之禁。迫在朝夕。臣等忝居首善之地。目见乱亡之兆。若畏威怵祸。终不敢一言。则不但无以有辞于后世。其负 圣朝菁莪之化者。无以赎其辜矣。兹敢略㬥前后事实。相率呼吁焉。第伏念 圣心一系先入是主。向来章奏。非不详陈。而 乙览瞥过。严批旋下。此必不少徐究而然也。今臣等不避鈇钺。犹且苦口而力争者。或冀日月之明。有所更照。斯文之运。得以回否也。兹事源委既长。辞说甚浩。虽以 圣学之高明。有难草草看了。断其是非。伏愿 圣上勿以静摄之有妨省览而不肯加察也。差待少安之时。间间留神。虽至旬月之久。必使事实融会。是非瞭然然后。 明赐处分。则臣等虽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万万无恨矣。呜呼。锡文辈之疏,凤辉等之劄出。而三朝宾师之大老。一代礼遇之儒贤。被蔑既极。谴罚随加。士林之痛恨骇愤。曷有其极哉。第伏见前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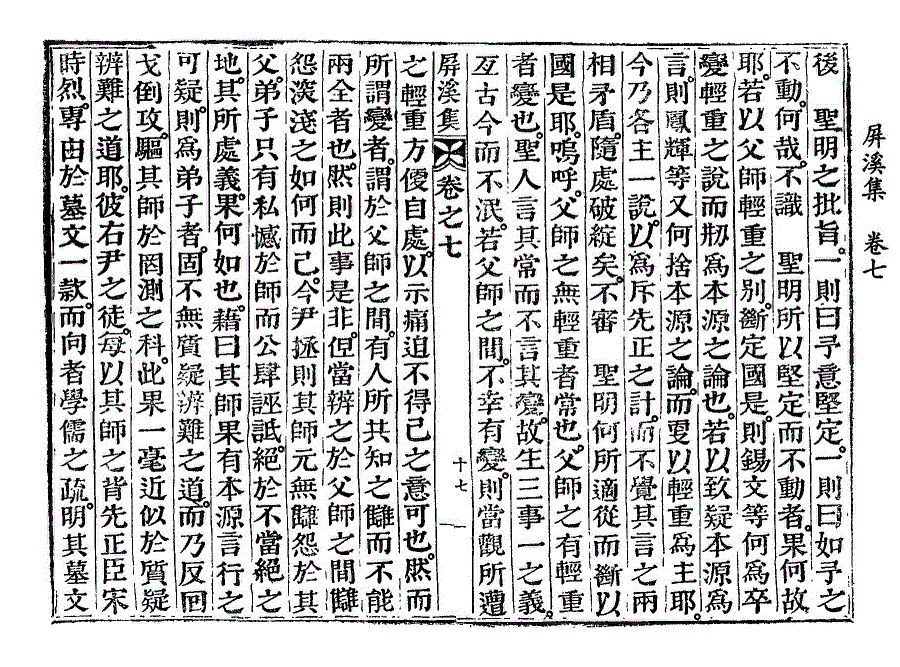 后 圣明之批旨。一则曰予意坚定。一则曰如予之不动。何哉。不识 圣明所以坚定而不动者。果何故耶。若以父师轻重之别。断定国是。则锡文等何为卒变轻重之说而刱为本源之论也。若以致疑本源为言。则凤辉等又何舍本源之论。而更以轻重为主耶。今乃各主一说。以为斥先正之计。而不觉其言之两相矛盾。随处破绽矣。不审 圣明何所适从而断以国是耶。呜呼。父师之无轻重者常也。父师之有轻重者变也。圣人言其常而不言其变。故生三事一之义。亘古今而不泯。若父师之间。不幸有变。则当观所遭之轻重方便自处。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然而所谓变者。谓于父师之间。有人所共知之雠而不能两全者也。然则此事是非。但当辨之于父师之间雠怨深浅之如何而已。今尹拯则其师元无雠怨于其父。弟子只有私憾于师而公肆诬诋。绝于不当绝之地。其所处义。果何如也。藉曰其师果有本源言行之可疑。则为弟子者。固不无质疑辨难之道。而乃反回戈倒攻。驱其师于罔测之科。此果一毫近似于质疑辨难之道耶。彼右尹之徒。每以其师之背先正臣宋时烈。专由于墓文一款。而向者学儒之疏。明其墓文
后 圣明之批旨。一则曰予意坚定。一则曰如予之不动。何哉。不识 圣明所以坚定而不动者。果何故耶。若以父师轻重之别。断定国是。则锡文等何为卒变轻重之说而刱为本源之论也。若以致疑本源为言。则凤辉等又何舍本源之论。而更以轻重为主耶。今乃各主一说。以为斥先正之计。而不觉其言之两相矛盾。随处破绽矣。不审 圣明何所适从而断以国是耶。呜呼。父师之无轻重者常也。父师之有轻重者变也。圣人言其常而不言其变。故生三事一之义。亘古今而不泯。若父师之间。不幸有变。则当观所遭之轻重方便自处。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然而所谓变者。谓于父师之间。有人所共知之雠而不能两全者也。然则此事是非。但当辨之于父师之间雠怨深浅之如何而已。今尹拯则其师元无雠怨于其父。弟子只有私憾于师而公肆诬诋。绝于不当绝之地。其所处义。果何如也。藉曰其师果有本源言行之可疑。则为弟子者。固不无质疑辨难之道。而乃反回戈倒攻。驱其师于罔测之科。此果一毫近似于质疑辨难之道耶。彼右尹之徒。每以其师之背先正臣宋时烈。专由于墓文一款。而向者学儒之疏。明其墓文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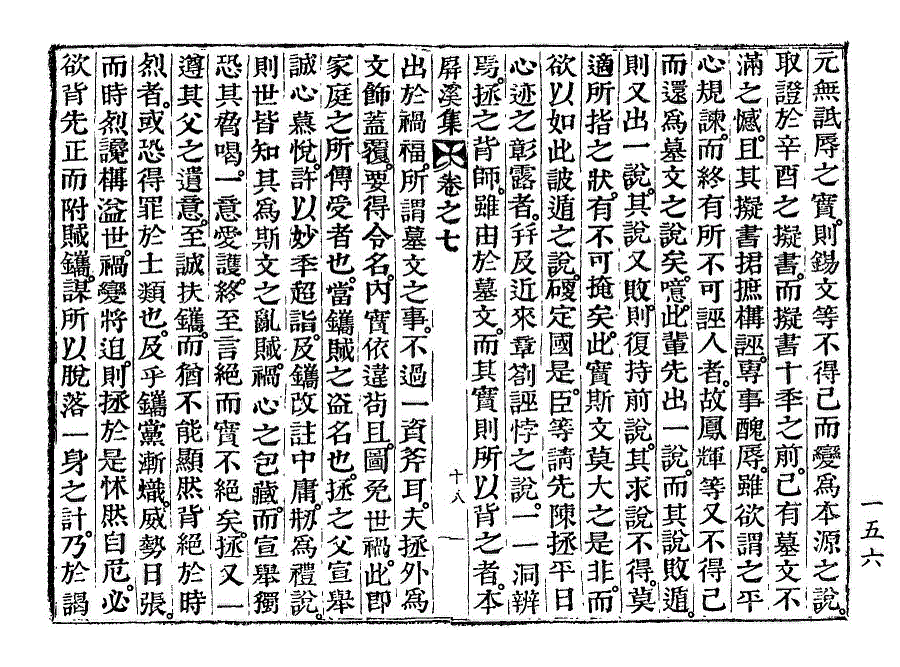 元无诋辱之实。则锡文等不得已而变为本源之说。取證于辛酉之拟书。而拟书十年之前。已有墓文不满之憾。且其拟书捃摭构诬。专事丑辱。虽欲谓之平心规谏。而终有所不可诬人者。故凤辉等又不得已而还为墓文之说矣。噫。此辈先出一说。而其说败遁。则又出一说。其说又败。则复持前说。其求说不得。莫适所指之状。有不可掩矣。此实斯文莫大之是非。而欲以如此诐遁之说。硬定国是。臣等请先陈拯平日心迹之彰露者。并及近来章劄诬悖之说。一一洞辨焉。拯之背师。虽由于墓文。而其实则所以背之者。本出于祸福。所谓墓文之事。不过一资斧耳。夫拯外为文饰盖覆。要得令名。内实依违苟且。图免世祸。此即家庭之所传受者也。当鑴贼之盗名也。拯之父宣举诚心慕悦。许以妙年超诣。及鑴改注中庸。刱为礼说。则世皆知其为斯文之乱贼。祸心之包藏。而宣举独恐其胁喝。一意爱护。终至言绝而实不绝矣。拯又一遵其父之遗意。至诚扶鑴。而犹不能显然背绝于时烈者。或恐得罪于士类也。及乎鑴党渐炽。威势日张。而时烈谗构溢世。祸变将迫。则拯于是怵然自危。必欲背先正而附贼鑴。谋所以脱落一身之计。乃于谒
元无诋辱之实。则锡文等不得已而变为本源之说。取證于辛酉之拟书。而拟书十年之前。已有墓文不满之憾。且其拟书捃摭构诬。专事丑辱。虽欲谓之平心规谏。而终有所不可诬人者。故凤辉等又不得已而还为墓文之说矣。噫。此辈先出一说。而其说败遁。则又出一说。其说又败。则复持前说。其求说不得。莫适所指之状。有不可掩矣。此实斯文莫大之是非。而欲以如此诐遁之说。硬定国是。臣等请先陈拯平日心迹之彰露者。并及近来章劄诬悖之说。一一洞辨焉。拯之背师。虽由于墓文。而其实则所以背之者。本出于祸福。所谓墓文之事。不过一资斧耳。夫拯外为文饰盖覆。要得令名。内实依违苟且。图免世祸。此即家庭之所传受者也。当鑴贼之盗名也。拯之父宣举诚心慕悦。许以妙年超诣。及鑴改注中庸。刱为礼说。则世皆知其为斯文之乱贼。祸心之包藏。而宣举独恐其胁喝。一意爱护。终至言绝而实不绝矣。拯又一遵其父之遗意。至诚扶鑴。而犹不能显然背绝于时烈者。或恐得罪于士类也。及乎鑴党渐炽。威势日张。而时烈谗构溢世。祸变将迫。则拯于是怵然自危。必欲背先正而附贼鑴。谋所以脱落一身之计。乃于谒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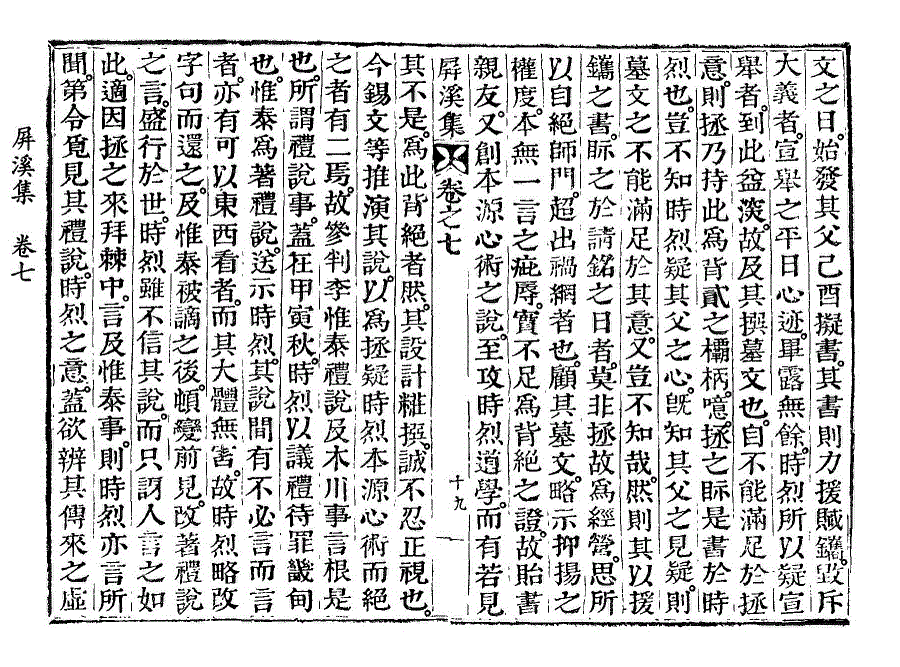 文之日。始发其父己酉拟书。其书则力援贼鑴。毁斥大义者。宣举之平日心迹。毕露无馀。时烈所以疑宣举者。到此益深。故及其撰墓文也。自不能满足于拯意。则拯乃持此为背贰之把柄。噫。拯之视是书于时烈也。岂不知时烈疑其父之心。既知其父之见疑。则墓文之不能满足于其意。又岂不知哉。然则其以援鑴之书。视之于请铭之日者。莫非拯故为经营。思所以自绝师门。超出祸网者也。顾其墓文。略示抑扬之权度。本无一言之疵辱。实不足为背绝之證。故贻书亲友。又创本源心术之说。至攻时烈道学。而有若见其不是。为此背绝者然。其设计妆撰。诚不忍正视也。今锡文等推演其说。以为拯疑时烈本源心术而绝之者有二焉。故参判李惟泰礼说及木川事言根是也。所谓礼说事。盖在甲寅秋。时烈以议礼待罪畿甸也。惟泰为著礼说。送示时烈。其说间有不必言而言者。亦有可以东西看者。而其大体无害。故时烈略改字句而还之。及惟泰被谪之后。顿变前见。改著礼说之言。盛行于世。时烈虽不信其说。而只讶人言之如此。适因拯之来拜棘中。言及惟泰事。则时烈亦言所闻。第令觅见其礼说。时烈之意。盖欲辨其传来之虚
文之日。始发其父己酉拟书。其书则力援贼鑴。毁斥大义者。宣举之平日心迹。毕露无馀。时烈所以疑宣举者。到此益深。故及其撰墓文也。自不能满足于拯意。则拯乃持此为背贰之把柄。噫。拯之视是书于时烈也。岂不知时烈疑其父之心。既知其父之见疑。则墓文之不能满足于其意。又岂不知哉。然则其以援鑴之书。视之于请铭之日者。莫非拯故为经营。思所以自绝师门。超出祸网者也。顾其墓文。略示抑扬之权度。本无一言之疵辱。实不足为背绝之證。故贻书亲友。又创本源心术之说。至攻时烈道学。而有若见其不是。为此背绝者然。其设计妆撰。诚不忍正视也。今锡文等推演其说。以为拯疑时烈本源心术而绝之者有二焉。故参判李惟泰礼说及木川事言根是也。所谓礼说事。盖在甲寅秋。时烈以议礼待罪畿甸也。惟泰为著礼说。送示时烈。其说间有不必言而言者。亦有可以东西看者。而其大体无害。故时烈略改字句而还之。及惟泰被谪之后。顿变前见。改著礼说之言。盛行于世。时烈虽不信其说。而只讶人言之如此。适因拯之来拜棘中。言及惟泰事。则时烈亦言所闻。第令觅见其礼说。时烈之意。盖欲辨其传来之虚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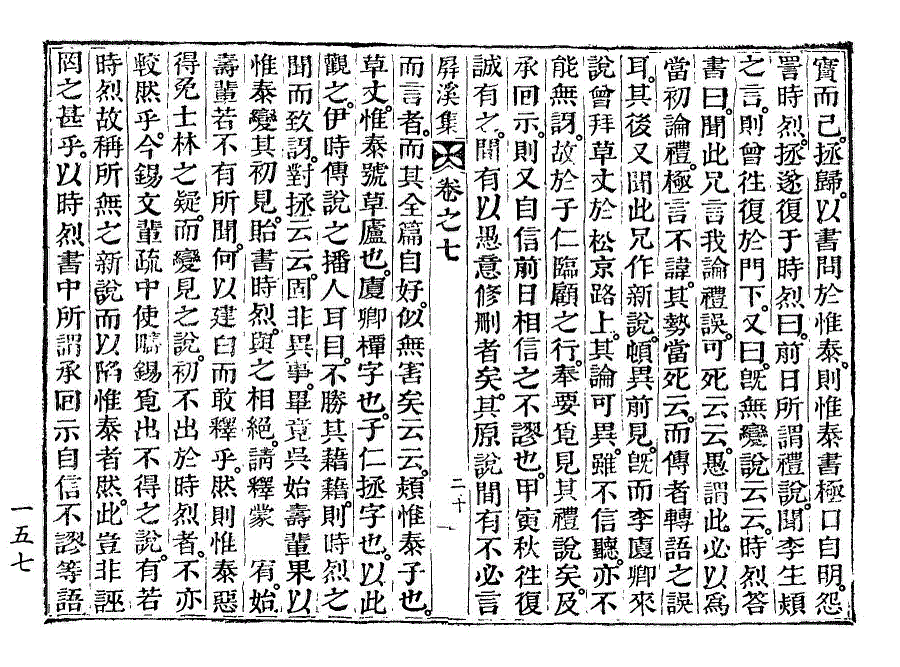 实而已。拯归。以书问于惟泰。则惟泰书极口自明。怨詈时烈。拯遂复于时烈曰。前日所谓礼说。闻李生颎之言。则曾往复于门下。又曰。既无变说云云。时烈答书曰。闻此兄言我论礼误。可死云云。愚谓此必以为当初论礼。极言不讳。其势当死云。而传者转语之误耳。其后又闻此兄作新说。顿异前见。既而李厦卿来说曾拜草丈于松京路上。其论可异。虽不信听。亦不能无讶。故于子仁临顾之行。奉要觅见其礼说矣。及承回示。则又自信前日相信之不谬也。甲寅秋往复诚有之。间有以愚意修删者矣。其原说间有不必言而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无害矣云云。颎惟泰子也。草丈。惟泰号草庐也。厦卿橝字也。子仁拯字也。以此观之。伊时传说之播人耳目。不胜其藉藉。则时烈之闻而致讶。对拯云云。固非异事。毕竟吴始寿辈果以惟泰变其初见。贻书时烈。与之相绝。请释蒙 宥。始寿辈若不有所闻。何以建白而敢释乎。然则惟泰恶得免士林之疑。而变见之说。初不出于时烈者。不亦较然乎。今锡文辈疏中使畴锡觅出不得之说。有若时烈故称所无之新说而以陷惟泰者然。此岂非诬罔之甚乎。以时烈书中所谓承回示自信不谬等语
实而已。拯归。以书问于惟泰。则惟泰书极口自明。怨詈时烈。拯遂复于时烈曰。前日所谓礼说。闻李生颎之言。则曾往复于门下。又曰。既无变说云云。时烈答书曰。闻此兄言我论礼误。可死云云。愚谓此必以为当初论礼。极言不讳。其势当死云。而传者转语之误耳。其后又闻此兄作新说。顿异前见。既而李厦卿来说曾拜草丈于松京路上。其论可异。虽不信听。亦不能无讶。故于子仁临顾之行。奉要觅见其礼说矣。及承回示。则又自信前日相信之不谬也。甲寅秋往复诚有之。间有以愚意修删者矣。其原说间有不必言而言者。而其全篇自好。似无害矣云云。颎惟泰子也。草丈。惟泰号草庐也。厦卿橝字也。子仁拯字也。以此观之。伊时传说之播人耳目。不胜其藉藉。则时烈之闻而致讶。对拯云云。固非异事。毕竟吴始寿辈果以惟泰变其初见。贻书时烈。与之相绝。请释蒙 宥。始寿辈若不有所闻。何以建白而敢释乎。然则惟泰恶得免士林之疑。而变见之说。初不出于时烈者。不亦较然乎。今锡文辈疏中使畴锡觅出不得之说。有若时烈故称所无之新说而以陷惟泰者然。此岂非诬罔之甚乎。以时烈书中所谓承回示自信不谬等语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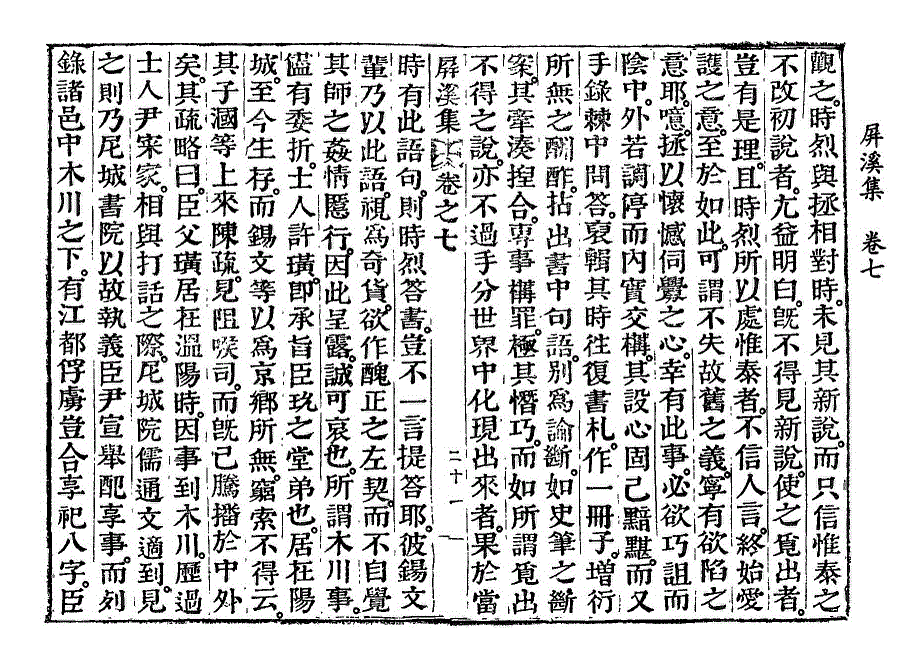 观之。时烈与拯相对时。未见其新说。而只信惟泰之不改初说者。尤益明白。既不得见新说。使之觅出者。岂有是理。且时烈所以处惟泰者。不信人言。终始爱护之意。至于如此。可谓不失故旧之义。宁有欲陷之意耶。噫。拯以怀憾伺衅之心。幸有此事。必欲巧诅而阴中。外若调停而内实交构。其设心固已黯黮。而又手录棘中问答。裒辑其时往复书札。作一册子。增衍所无之酬酢。拈出书中句语。别为论断。如史笔之断案。其牵凑捏合。专事构罪。极其憯巧。而如所谓觅出不得之说。亦不过手分世界中化现出来者。果于当时有此语句。则时烈答书。岂不一言提答耶。彼锡文辈乃以此语。视为奇货。欲作丑正之左契。而不自觉其师之奸情慝行。因此呈露。诚可哀也。所谓木川事。尽有委折。士人许璜。即承旨臣玧之堂弟也。居在阳城。至今生存。而锡文等以为京乡所无。穷索不得云。其子漍等上来陈疏。见阻喉司。而既已腾播于中外矣。其疏略曰。臣父璜居在温阳时。因事到木川。历过士人尹寀家。相与打话之际。尼城院儒通文适到。见之则乃尼城书院以故执义臣尹宣举配享事。而列录诸邑中木川之下。有江都俘虏岂合享祀八字。臣
观之。时烈与拯相对时。未见其新说。而只信惟泰之不改初说者。尤益明白。既不得见新说。使之觅出者。岂有是理。且时烈所以处惟泰者。不信人言。终始爱护之意。至于如此。可谓不失故旧之义。宁有欲陷之意耶。噫。拯以怀憾伺衅之心。幸有此事。必欲巧诅而阴中。外若调停而内实交构。其设心固已黯黮。而又手录棘中问答。裒辑其时往复书札。作一册子。增衍所无之酬酢。拈出书中句语。别为论断。如史笔之断案。其牵凑捏合。专事构罪。极其憯巧。而如所谓觅出不得之说。亦不过手分世界中化现出来者。果于当时有此语句。则时烈答书。岂不一言提答耶。彼锡文辈乃以此语。视为奇货。欲作丑正之左契。而不自觉其师之奸情慝行。因此呈露。诚可哀也。所谓木川事。尽有委折。士人许璜。即承旨臣玧之堂弟也。居在阳城。至今生存。而锡文等以为京乡所无。穷索不得云。其子漍等上来陈疏。见阻喉司。而既已腾播于中外矣。其疏略曰。臣父璜居在温阳时。因事到木川。历过士人尹寀家。相与打话之际。尼城院儒通文适到。见之则乃尼城书院以故执义臣尹宣举配享事。而列录诸邑中木川之下。有江都俘虏岂合享祀八字。臣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8L 页
 父于还家后。见同里士人赵文宙,韩尚谦。说及此事。则答曰。君果得见耶。吾辈亦闻之矣云云。厥后湖中士人。无不传说。及至辛酉春。先正来住水原万义地。臣父即往拜。偶以通文中木川下八字之说提及。则先正曰。果如君言。则木川风习。诚可寒心。逮夫先正还归之时。臣父仍随往行到德坪。李翔亦自全义来迎。先正谓翔曰。闻木人丑辱美村。其习可恶。公为院长。能化之乎云。而仍以所闻于臣父者言之。其时臣父在座参听。故详记如此云云。美村宣举号也。盖其时李翔闻先正之言。欲使院儒摘罚。则人多致疑于柳寿芳。而木人深讳固隐。有难的知。必考其笔迹然后。可以得其人。故通文尼城。还索其文。则尼儒答曰。佥尊尊贤之诚。不胜钦仰。第已过之事。不必更起闹端。木儒再通。则又答以元无悬录之事云。其前后所答。自相牴牾。盖其意欲讳隐之也。自是之后。拯不怒木人。而移怒于先正之传说。累度贻书。迫问其言根于先正。则先正不得已遂举许璜以證之。漍等疏谓其父与尹自少相熟云。而拯一不问之于璜。而勒归之于先正之自做自播者。抑独何心。而今以见存之人。直谓之亡。是其欺诬 天听。若是无忌。则其他诪
父于还家后。见同里士人赵文宙,韩尚谦。说及此事。则答曰。君果得见耶。吾辈亦闻之矣云云。厥后湖中士人。无不传说。及至辛酉春。先正来住水原万义地。臣父即往拜。偶以通文中木川下八字之说提及。则先正曰。果如君言。则木川风习。诚可寒心。逮夫先正还归之时。臣父仍随往行到德坪。李翔亦自全义来迎。先正谓翔曰。闻木人丑辱美村。其习可恶。公为院长。能化之乎云。而仍以所闻于臣父者言之。其时臣父在座参听。故详记如此云云。美村宣举号也。盖其时李翔闻先正之言。欲使院儒摘罚。则人多致疑于柳寿芳。而木人深讳固隐。有难的知。必考其笔迹然后。可以得其人。故通文尼城。还索其文。则尼儒答曰。佥尊尊贤之诚。不胜钦仰。第已过之事。不必更起闹端。木儒再通。则又答以元无悬录之事云。其前后所答。自相牴牾。盖其意欲讳隐之也。自是之后。拯不怒木人。而移怒于先正之传说。累度贻书。迫问其言根于先正。则先正不得已遂举许璜以證之。漍等疏谓其父与尹自少相熟云。而拯一不问之于璜。而勒归之于先正之自做自播者。抑独何心。而今以见存之人。直谓之亡。是其欺诬 天听。若是无忌。则其他诪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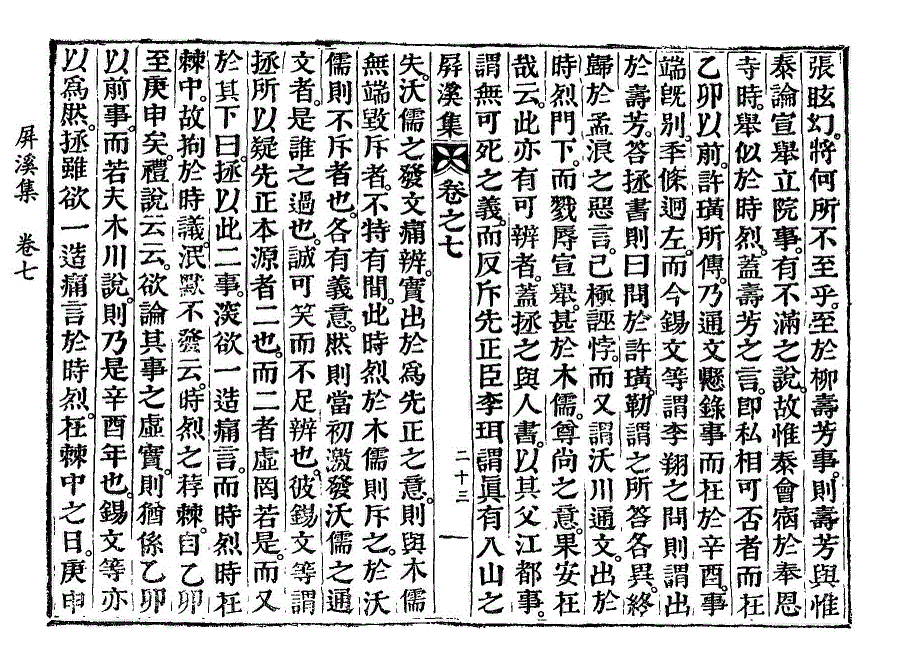 张眩幻。将何所不至乎。至于柳寿芳事。则寿芳与惟泰论宣举立院事。有不满之说。故惟泰会宿于奉恩寺时。举似于时烈。盖寿芳之言。即私相可否者而在乙卯以前。许璜所传。乃通文悬录事而在于辛酉。事端既别。年条迥左。而今锡文等谓李翔之问则谓出于寿芳。答拯书则曰问于许璜。勒谓之所答各异。终归于孟浪之恶言。已极诬悖。而又谓沃川通文。出于时烈门下。而戮辱宣举。甚于木儒。尊尚之意。果安在哉云。此亦有可辨者。盖拯之与人书。以其父江都事。谓无可死之义。而反斥先正臣李珥谓真有入山之失。沃儒之发文痛辨。实出于为先正之意。则与木儒无端毁斥者。不特有间。此时烈于木儒则斥之。于沃儒则不斥者也。各有义意。然则当初激发沃儒之通文者。是谁之过也。诚可笑而不足辨也。彼锡文等谓拯所以疑先正本源者二也。而二者虚罔若是。而又于其下曰。拯以此二事。深欲一造痛言。而时烈时在棘中。故拘于时议。泯默不发云。时烈之荐棘。自乙卯至庚申矣。礼说云云。欲论其事之虚实。则犹系乙卯以前事。而若夫木川说。则乃是辛酉年也。锡文等亦以为然。拯虽欲一造痛言于时烈。在棘中之日。庚申
张眩幻。将何所不至乎。至于柳寿芳事。则寿芳与惟泰论宣举立院事。有不满之说。故惟泰会宿于奉恩寺时。举似于时烈。盖寿芳之言。即私相可否者而在乙卯以前。许璜所传。乃通文悬录事而在于辛酉。事端既别。年条迥左。而今锡文等谓李翔之问则谓出于寿芳。答拯书则曰问于许璜。勒谓之所答各异。终归于孟浪之恶言。已极诬悖。而又谓沃川通文。出于时烈门下。而戮辱宣举。甚于木儒。尊尚之意。果安在哉云。此亦有可辨者。盖拯之与人书。以其父江都事。谓无可死之义。而反斥先正臣李珥谓真有入山之失。沃儒之发文痛辨。实出于为先正之意。则与木儒无端毁斥者。不特有间。此时烈于木儒则斥之。于沃儒则不斥者也。各有义意。然则当初激发沃儒之通文者。是谁之过也。诚可笑而不足辨也。彼锡文等谓拯所以疑先正本源者二也。而二者虚罔若是。而又于其下曰。拯以此二事。深欲一造痛言。而时烈时在棘中。故拘于时议。泯默不发云。时烈之荐棘。自乙卯至庚申矣。礼说云云。欲论其事之虚实。则犹系乙卯以前事。而若夫木川说。则乃是辛酉年也。锡文等亦以为然。拯虽欲一造痛言于时烈。在棘中之日。庚申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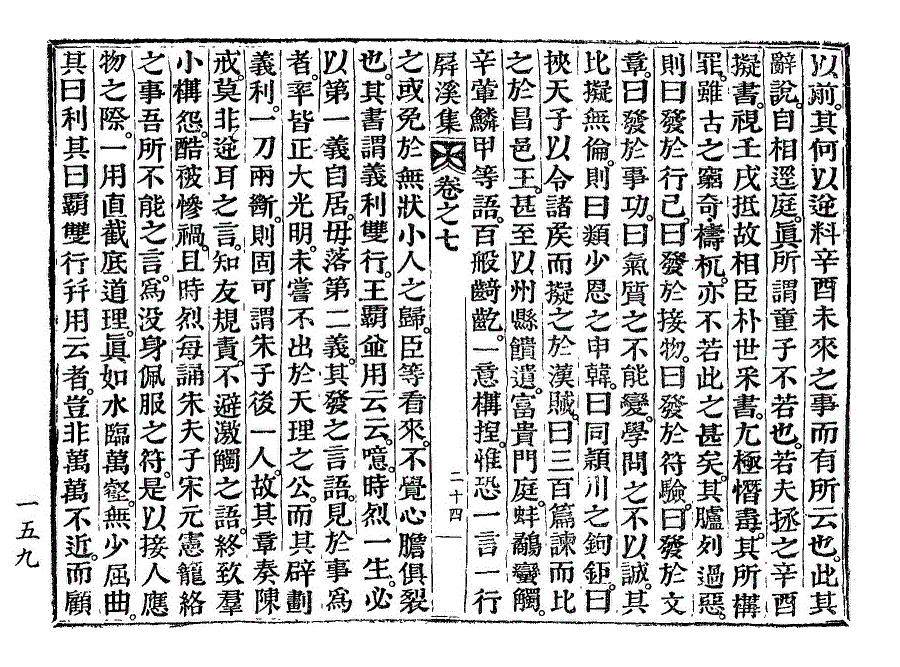 以前。其何以逆料辛酉未来之事而有所云也。此其辞说。自相径庭。真所谓童子不若也。若夫拯之辛酉拟书。视壬戌抵故相臣朴世采书。尤极憯毒。其所构罪。虽古之穷奇,梼杌。亦不若此之甚矣。其胪列过恶。则曰发于行己。曰发于接物。曰发于符验。曰发于文章。曰发于事功。曰气质之不能变。学问之不以诚。其比拟无伦。则曰类少恩之申韩。曰同颖川之钩钜。曰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拟之于汉贼。曰三百篇谏而比之于昌邑王。甚至以州县馈遗。富贵门庭。蚌鹬蛮触。辛荤鳞甲等语。百般齮龁。一意构捏。惟恐一言一行之或免于无状小人之归。臣等看来。不觉心胆俱裂也。其书谓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云云。噫。时烈一生。必以第一义自居。毋落第二义。其发之言语。见于事为者。率皆正大光明。未尝不出于天理之公。而其辟划义利。一刀两断。则固可谓朱子后一人。故其章奏陈戒。莫非逆耳之言。知友规责。不避激触之语。终致群小构怨。酷被惨祸。且时烈每诵朱夫子宋元宪笼络之事吾所不能之言。为没身佩服之符。是以接人应物之际。一用直截底道理。真如水临万壑。无少屈曲。其曰利其曰霸双行并用云者。岂非万万不近。而顾
以前。其何以逆料辛酉未来之事而有所云也。此其辞说。自相径庭。真所谓童子不若也。若夫拯之辛酉拟书。视壬戌抵故相臣朴世采书。尤极憯毒。其所构罪。虽古之穷奇,梼杌。亦不若此之甚矣。其胪列过恶。则曰发于行己。曰发于接物。曰发于符验。曰发于文章。曰发于事功。曰气质之不能变。学问之不以诚。其比拟无伦。则曰类少恩之申韩。曰同颖川之钩钜。曰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拟之于汉贼。曰三百篇谏而比之于昌邑王。甚至以州县馈遗。富贵门庭。蚌鹬蛮触。辛荤鳞甲等语。百般齮龁。一意构捏。惟恐一言一行之或免于无状小人之归。臣等看来。不觉心胆俱裂也。其书谓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云云。噫。时烈一生。必以第一义自居。毋落第二义。其发之言语。见于事为者。率皆正大光明。未尝不出于天理之公。而其辟划义利。一刀两断。则固可谓朱子后一人。故其章奏陈戒。莫非逆耳之言。知友规责。不避激触之语。终致群小构怨。酷被惨祸。且时烈每诵朱夫子宋元宪笼络之事吾所不能之言。为没身佩服之符。是以接人应物之际。一用直截底道理。真如水临万壑。无少屈曲。其曰利其曰霸双行并用云者。岂非万万不近。而顾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0H 页
 奚异于指伯夷而谓盗蹠也。其书又谓引绳从违于一言之异同。一事之差互。又谓以同异为亲疏。以好恶为彼此。噫。苟君子也。亲而好之。苟小人也。疏而恶之。其所以亲而好者。非为同于己也。为其合于君子故也。其所以疏而恶之者。非为异于己也。为其归于小人故也。然则引绳从违之间。可见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矣。岂必鹘突吞枣。依违苟且。若亲若疏。无彼无此然后。乃可谓真正道理耶。此则自有一种家法。而世之自好者耻之。况以时烈之正大光明。其肯为此耶。至若违拂者有患。将顺者无灾。歆动以势。怵迫以威云者。此正奸臣之得志用权者事。而乃敢肆然勒加。是可忍欤。噫。时烈积困群小。半生齮龁。尚不得庇其一身。宁有灾患之所由生。而亦安有威势之可论也。若其承百代儒门之统。负一世山斗之望。朝野想望。士林向风者。诚有之矣。今以钦仰德义。一意尊奉为歆动。而严畏公议。不敢崖异为怵迫。则孔孟程朱之为天下后世之所景慕。无或非议者。亦将谓威势之所使然耶。其书又谓自处偏于刚峻一边。而责人猛为峻。力服人为刚。又谓平生情义。弃之如遗。又谓平生亲旧。无一人全其终始。噫。凡此云云。岂指
奚异于指伯夷而谓盗蹠也。其书又谓引绳从违于一言之异同。一事之差互。又谓以同异为亲疏。以好恶为彼此。噫。苟君子也。亲而好之。苟小人也。疏而恶之。其所以亲而好者。非为同于己也。为其合于君子故也。其所以疏而恶之者。非为异于己也。为其归于小人故也。然则引绳从违之间。可见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矣。岂必鹘突吞枣。依违苟且。若亲若疏。无彼无此然后。乃可谓真正道理耶。此则自有一种家法。而世之自好者耻之。况以时烈之正大光明。其肯为此耶。至若违拂者有患。将顺者无灾。歆动以势。怵迫以威云者。此正奸臣之得志用权者事。而乃敢肆然勒加。是可忍欤。噫。时烈积困群小。半生齮龁。尚不得庇其一身。宁有灾患之所由生。而亦安有威势之可论也。若其承百代儒门之统。负一世山斗之望。朝野想望。士林向风者。诚有之矣。今以钦仰德义。一意尊奉为歆动。而严畏公议。不敢崖异为怵迫。则孔孟程朱之为天下后世之所景慕。无或非议者。亦将谓威势之所使然耶。其书又谓自处偏于刚峻一边。而责人猛为峻。力服人为刚。又谓平生情义。弃之如遗。又谓平生亲旧。无一人全其终始。噫。凡此云云。岂指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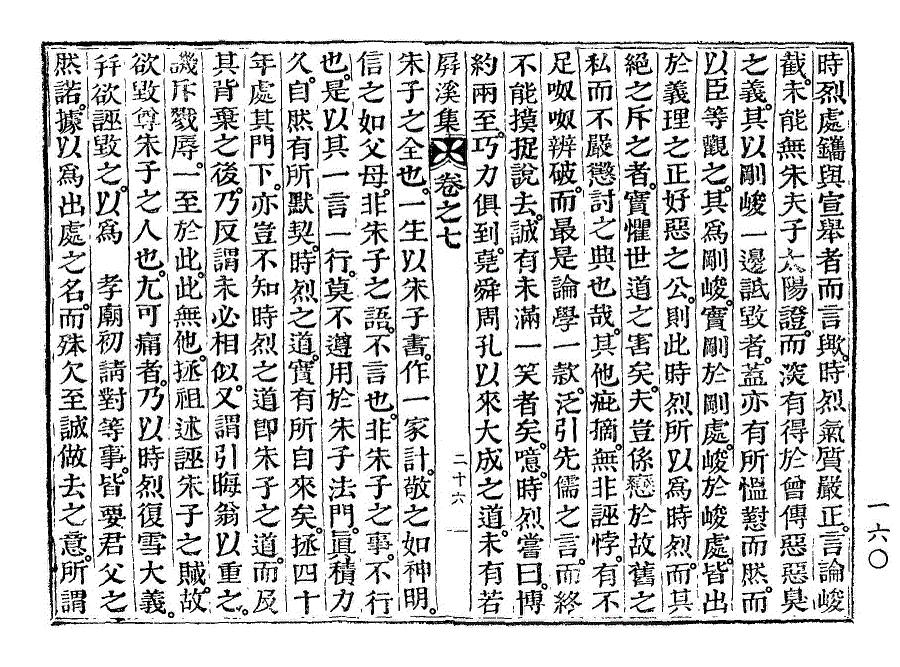 时烈处鑴与宣举者而言欤。时烈气质严正。言论峻截。未能无朱夫子太阳證。而深有得于曾传恶恶臭之义。其以刚峻一边诋毁者。盖亦有所愠怼而然。而以臣等观之。其为刚峻。实刚于刚处。峻于峻处。皆出于义理之正好恶之公。则此时烈所以为时烈。而其绝之斥之者。实惧世道之害矣。夫岂系恋于故旧之私而不严惩讨之典也哉。其他疵摘。无非诬悖。有不足呶呶辨破。而最是论学一款。泛引先儒之言。而终不能摸捉说去。诚有未满一笑者矣。噫。时烈尝曰。博约两至。巧力俱到。尧舜周孔以来大成之道。未有若朱子之全也。一生以朱子书。作一家计。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非朱子之语。不言也。非朱子之事。不行也。是以其一言一行。莫不遵用于朱子法门。真积力久。自然有所默契。时烈之道。实有所自来矣。拯四十年处其门下。亦岂不知时烈之道即朱子之道。而及其背弃之后。乃反谓未必相似。又谓引晦翁以重之。讥斥戮辱。一至于此。此无他。拯祖述诬朱子之贼。故欲毁尊朱子之人也。尤可痛者。乃以时烈复雪大义。并欲诬毁之。以为 孝庙初请对等事。皆要君父之然诺。据以为出处之名。而殊欠至诚做去之意。所谓
时烈处鑴与宣举者而言欤。时烈气质严正。言论峻截。未能无朱夫子太阳證。而深有得于曾传恶恶臭之义。其以刚峻一边诋毁者。盖亦有所愠怼而然。而以臣等观之。其为刚峻。实刚于刚处。峻于峻处。皆出于义理之正好恶之公。则此时烈所以为时烈。而其绝之斥之者。实惧世道之害矣。夫岂系恋于故旧之私而不严惩讨之典也哉。其他疵摘。无非诬悖。有不足呶呶辨破。而最是论学一款。泛引先儒之言。而终不能摸捉说去。诚有未满一笑者矣。噫。时烈尝曰。博约两至。巧力俱到。尧舜周孔以来大成之道。未有若朱子之全也。一生以朱子书。作一家计。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非朱子之语。不言也。非朱子之事。不行也。是以其一言一行。莫不遵用于朱子法门。真积力久。自然有所默契。时烈之道。实有所自来矣。拯四十年处其门下。亦岂不知时烈之道即朱子之道。而及其背弃之后。乃反谓未必相似。又谓引晦翁以重之。讥斥戮辱。一至于此。此无他。拯祖述诬朱子之贼。故欲毁尊朱子之人也。尤可痛者。乃以时烈复雪大义。并欲诬毁之。以为 孝庙初请对等事。皆要君父之然诺。据以为出处之名。而殊欠至诚做去之意。所谓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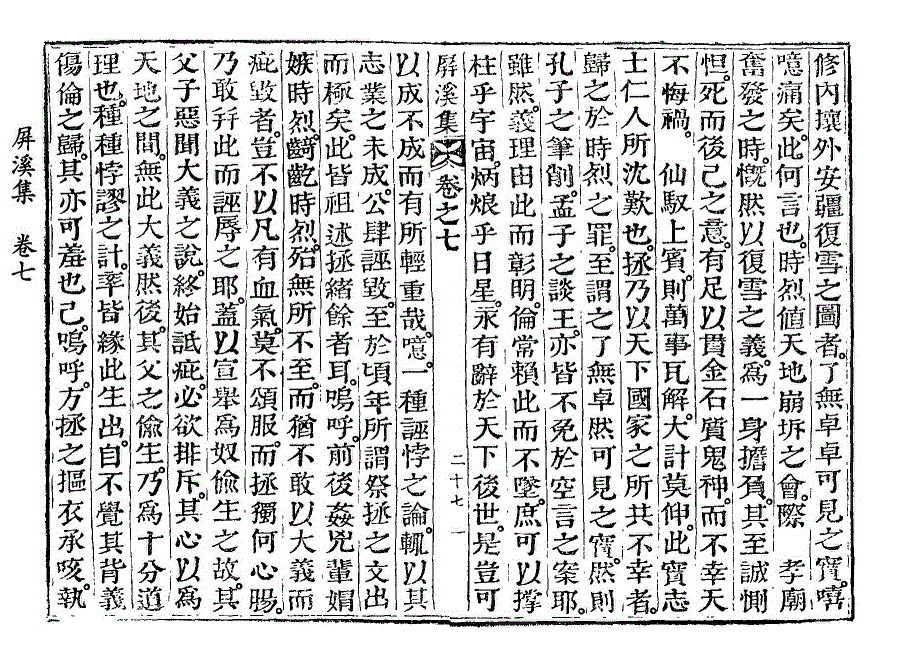 修内攘外安疆复雪之图者。了无卓卓可见之实。嘻噫痛矣。此何言也。时烈值天地崩坼之会。际 孝庙奋发之时。慨然以复雪之义。为一身担负。其至诚恻怛。死而后已之意。有足以贯金石质鬼神。而不幸天不悔祸。 仙驭上宾。则万事瓦解。大计莫伸。此实志士仁人所沈叹也。拯乃以天下国家之所共不幸者。归之于时烈之罪。至谓之了无卓然可见之实。然则孔子之笔削。孟子之谈王。亦皆不免于空言之案耶。虽然。义理由此而彰明。伦常赖此而不坠。庶可以撑柱乎宇宙。炳烺乎日星。永有辞于天下后世。是岂可以成不成而有所轻重哉。噫。一种诬悖之论。辄以其志业之未成。公肆诬毁。至于顷年所谓祭拯之文出而极矣。此皆祖述拯绪馀者耳。呜呼。前后奸凶辈媢嫉时烈。齮龁时烈。殆无所不至。而犹不敢以大义而疵毁者。岂不以凡有血气。莫不颂服。而拯独何心肠。乃敢并此而诬辱之耶。盖以宣举为奴偷生之故。其父子恶闻大义之说。终始诋疵。必欲排斥。其心以为天地之间。无此大义然后。其父之偷生。乃为十分道理也。种种悖谬之计。率皆缘此生出。自不觉其背义伤伦之归。其亦可羞也已。呜呼。方拯之抠衣承咳。执
修内攘外安疆复雪之图者。了无卓卓可见之实。嘻噫痛矣。此何言也。时烈值天地崩坼之会。际 孝庙奋发之时。慨然以复雪之义。为一身担负。其至诚恻怛。死而后已之意。有足以贯金石质鬼神。而不幸天不悔祸。 仙驭上宾。则万事瓦解。大计莫伸。此实志士仁人所沈叹也。拯乃以天下国家之所共不幸者。归之于时烈之罪。至谓之了无卓然可见之实。然则孔子之笔削。孟子之谈王。亦皆不免于空言之案耶。虽然。义理由此而彰明。伦常赖此而不坠。庶可以撑柱乎宇宙。炳烺乎日星。永有辞于天下后世。是岂可以成不成而有所轻重哉。噫。一种诬悖之论。辄以其志业之未成。公肆诬毁。至于顷年所谓祭拯之文出而极矣。此皆祖述拯绪馀者耳。呜呼。前后奸凶辈媢嫉时烈。齮龁时烈。殆无所不至。而犹不敢以大义而疵毁者。岂不以凡有血气。莫不颂服。而拯独何心肠。乃敢并此而诬辱之耶。盖以宣举为奴偷生之故。其父子恶闻大义之说。终始诋疵。必欲排斥。其心以为天地之间。无此大义然后。其父之偷生。乃为十分道理也。种种悖谬之计。率皆缘此生出。自不觉其背义伤伦之归。其亦可羞也已。呜呼。方拯之抠衣承咳。执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1L 页
 业请益也。唯诺惟谨。视师犹父。而及其背绝之心萌而构捏之计深。则壁立之岩岩气像。以为㬥厉。平生之卓卓大义。指谓假仁。以至忠告善谕。反为疑怒之端。谈经讲理。率归诟辱之资。以此言之。其四十年从游函丈。明着眼目者。只拟成得一副当声罪而已。揆以恒情。是岂忍为者耶。自夫此书之出。虽其阿好之辈。亦莫不惊怪愕眙。至有以为锡文之轻发为咎者。以 殿下高明之见。岂不觑得到底耶。锡文辈乃以此为出于至诚规谏。拟之于忠臣争子。此可谓病风之说也。昔刘淳叟尝从游于陆九渊。后对朱子。极辨九渊学术之谬。朱子责之曰。子静学术。自当付公议。公何敢如此。后来淳叟之狼狈。朱子举此事而言其质薄矣。夫陆氏之学。乃异端之尤者。淳叟之排。可谓能言拒杨墨。而朱子犹责之者。岂不以师之学术。非门生所可议耶。然则假使时烈真有学术之病。一如拯言。犹不可私议于人。况可以百端构捏。又因此而绝之乎。锡文等又举世采之言。谓世采以拯此书为好。而特以时烈无受人之量。故挽而不送云。何其诬也。世采抵拯书曰。窃观前日长书五六条。盖举其平生而道之。虽曰箴规。实则非斥也云云。拯之挟憾构
业请益也。唯诺惟谨。视师犹父。而及其背绝之心萌而构捏之计深。则壁立之岩岩气像。以为㬥厉。平生之卓卓大义。指谓假仁。以至忠告善谕。反为疑怒之端。谈经讲理。率归诟辱之资。以此言之。其四十年从游函丈。明着眼目者。只拟成得一副当声罪而已。揆以恒情。是岂忍为者耶。自夫此书之出。虽其阿好之辈。亦莫不惊怪愕眙。至有以为锡文之轻发为咎者。以 殿下高明之见。岂不觑得到底耶。锡文辈乃以此为出于至诚规谏。拟之于忠臣争子。此可谓病风之说也。昔刘淳叟尝从游于陆九渊。后对朱子。极辨九渊学术之谬。朱子责之曰。子静学术。自当付公议。公何敢如此。后来淳叟之狼狈。朱子举此事而言其质薄矣。夫陆氏之学。乃异端之尤者。淳叟之排。可谓能言拒杨墨。而朱子犹责之者。岂不以师之学术。非门生所可议耶。然则假使时烈真有学术之病。一如拯言。犹不可私议于人。况可以百端构捏。又因此而绝之乎。锡文等又举世采之言。谓世采以拯此书为好。而特以时烈无受人之量。故挽而不送云。何其诬也。世采抵拯书曰。窃观前日长书五六条。盖举其平生而道之。虽曰箴规。实则非斥也云云。拯之挟憾构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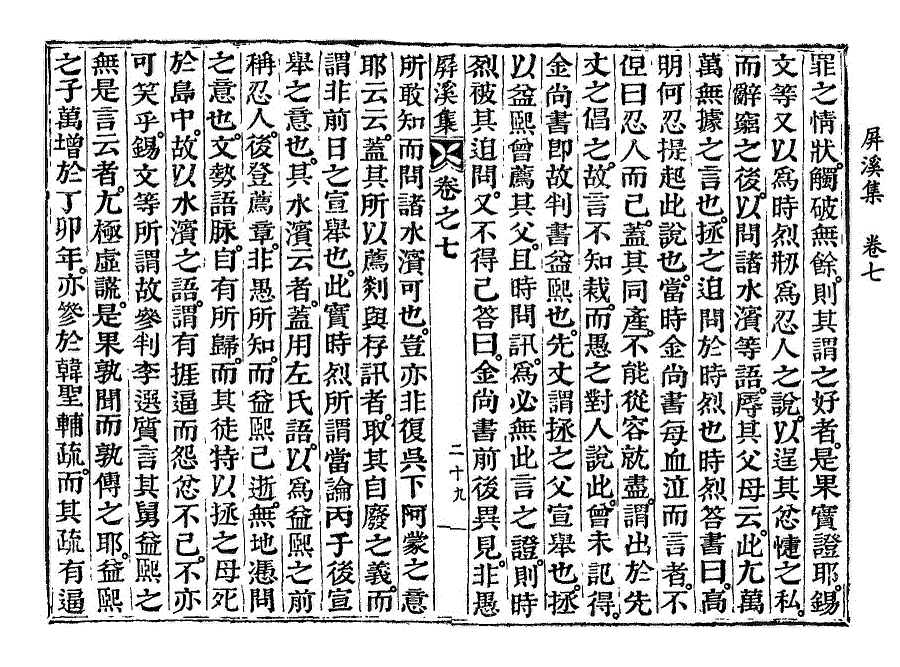 罪之情状。触破无馀。则其谓之好者。是果实證耶。锡文等又以为时烈刱为忍人之说。以逞其忿懥之私。而辞穷之后。以问诸水滨等语。辱其父母云。此尤万万无据之言也。拯之迫问于时烈也时烈答书曰。高明何忍提起此说也。当时金尚书每血泣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盖其同产。不能从容就尽。谓出于先丈之倡之。故言不知裁。而愚之对人说此。曾未记得。金尚书即故判书益熙也。先丈谓拯之父宣举也。拯以益熙曾荐其父。且时问讯。为必无此言之證。则时烈被其迫问。又不得已答曰。金尚书前后异见。非愚所敢知而问诸水滨可也。岂亦非复吴下阿蒙之意耶云云。盖其所以荐剡与存讯者。取其自废之义。而谓非前日之宣举也。此实时烈所谓当论丙子后宣举之意也。其水滨云者。盖用左氏语。以为益熙之前称忍人。后登荐章。非愚所知。而益熙已逝。无地凭问之意也。文势语脉。自有所归。而其徒特以拯之母死于岛中。故以水滨之语。谓有挨逼而怨忿不已。不亦可笑乎。锡文等所谓故参判李选质言其舅益熙之无是言云者。尤极虚谎。是果孰闻而孰传之耶。益熙之子万增于丁卯年。亦参于韩圣辅疏。而其疏有逼
罪之情状。触破无馀。则其谓之好者。是果实證耶。锡文等又以为时烈刱为忍人之说。以逞其忿懥之私。而辞穷之后。以问诸水滨等语。辱其父母云。此尤万万无据之言也。拯之迫问于时烈也时烈答书曰。高明何忍提起此说也。当时金尚书每血泣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盖其同产。不能从容就尽。谓出于先丈之倡之。故言不知裁。而愚之对人说此。曾未记得。金尚书即故判书益熙也。先丈谓拯之父宣举也。拯以益熙曾荐其父。且时问讯。为必无此言之證。则时烈被其迫问。又不得已答曰。金尚书前后异见。非愚所敢知而问诸水滨可也。岂亦非复吴下阿蒙之意耶云云。盖其所以荐剡与存讯者。取其自废之义。而谓非前日之宣举也。此实时烈所谓当论丙子后宣举之意也。其水滨云者。盖用左氏语。以为益熙之前称忍人。后登荐章。非愚所知。而益熙已逝。无地凭问之意也。文势语脉。自有所归。而其徒特以拯之母死于岛中。故以水滨之语。谓有挨逼而怨忿不已。不亦可笑乎。锡文等所谓故参判李选质言其舅益熙之无是言云者。尤极虚谎。是果孰闻而孰传之耶。益熙之子万增于丁卯年。亦参于韩圣辅疏。而其疏有逼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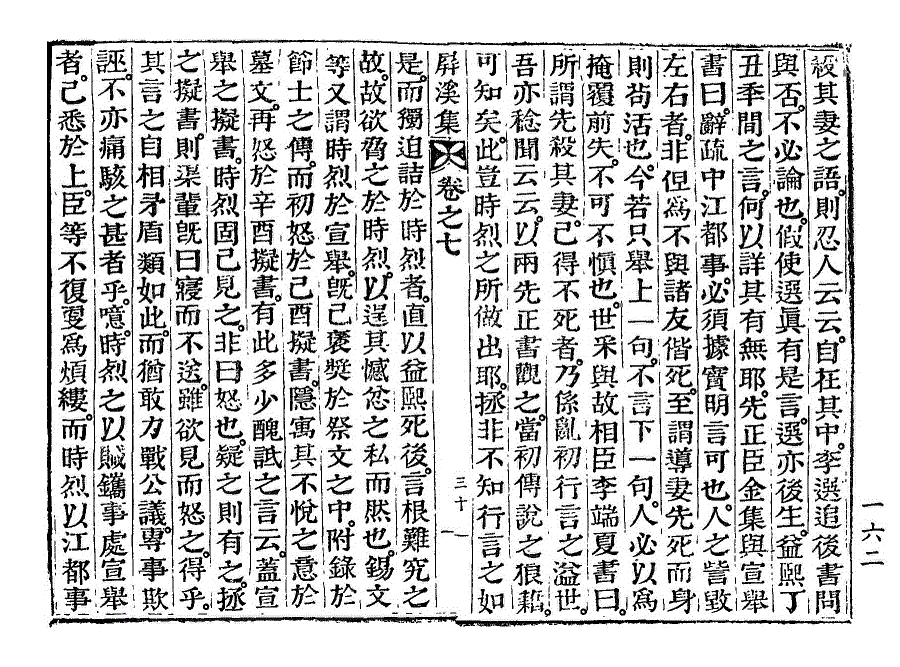 杀其妻之语。则忍人云云。自在其中。李选追后书问与否。不必论也。假使选真有是言。选亦后生。益熙丁丑年间之言。何以详其有无耶。先正臣金集与宣举书曰。辞疏中江都事。必须据实明言可也。人之訾毁左右者。非但为不与诸友偕死。至谓导妻先死而身则苟活也。今若只举上一句。不言下一句。人必以为掩覆前失。不可不慎也。世采与故相臣李端夏书曰。所谓先杀其妻。己得不死者。乃系乱初行言之溢世。吾亦稔闻云云。以两先正书观之。当初传说之狼藉。可知矣。此岂时烈之所做出耶。拯非不知行言之如是。而独迫诘于时烈者。直以益熙死后。言根难究之故。故欲胁之于时烈。以逞其憾忿之私而然也。锡文等又谓时烈于宣举。既已褒奖于祭文之中。附录于节士之传。而初怒于己酉拟书。隐寓其不悦之意于墓文。再怒于辛酉拟书。有此多少丑诋之言云。盖宣举之拟书。时烈固已见之。非曰怒也。疑之则有之。拯之拟书。则渠辈既曰寝而不送。虽欲见而怒之。得乎。其言之自相矛盾类如此。而犹敢力战公议。专事欺诬。不亦痛骇之甚者乎。噫。时烈之以贼鑴事处宣举者。已悉于上。臣等不复更为烦缕。而时烈以江都事
杀其妻之语。则忍人云云。自在其中。李选追后书问与否。不必论也。假使选真有是言。选亦后生。益熙丁丑年间之言。何以详其有无耶。先正臣金集与宣举书曰。辞疏中江都事。必须据实明言可也。人之訾毁左右者。非但为不与诸友偕死。至谓导妻先死而身则苟活也。今若只举上一句。不言下一句。人必以为掩覆前失。不可不慎也。世采与故相臣李端夏书曰。所谓先杀其妻。己得不死者。乃系乱初行言之溢世。吾亦稔闻云云。以两先正书观之。当初传说之狼藉。可知矣。此岂时烈之所做出耶。拯非不知行言之如是。而独迫诘于时烈者。直以益熙死后。言根难究之故。故欲胁之于时烈。以逞其憾忿之私而然也。锡文等又谓时烈于宣举。既已褒奖于祭文之中。附录于节士之传。而初怒于己酉拟书。隐寓其不悦之意于墓文。再怒于辛酉拟书。有此多少丑诋之言云。盖宣举之拟书。时烈固已见之。非曰怒也。疑之则有之。拯之拟书。则渠辈既曰寝而不送。虽欲见而怒之。得乎。其言之自相矛盾类如此。而犹敢力战公议。专事欺诬。不亦痛骇之甚者乎。噫。时烈之以贼鑴事处宣举者。已悉于上。臣等不复更为烦缕。而时烈以江都事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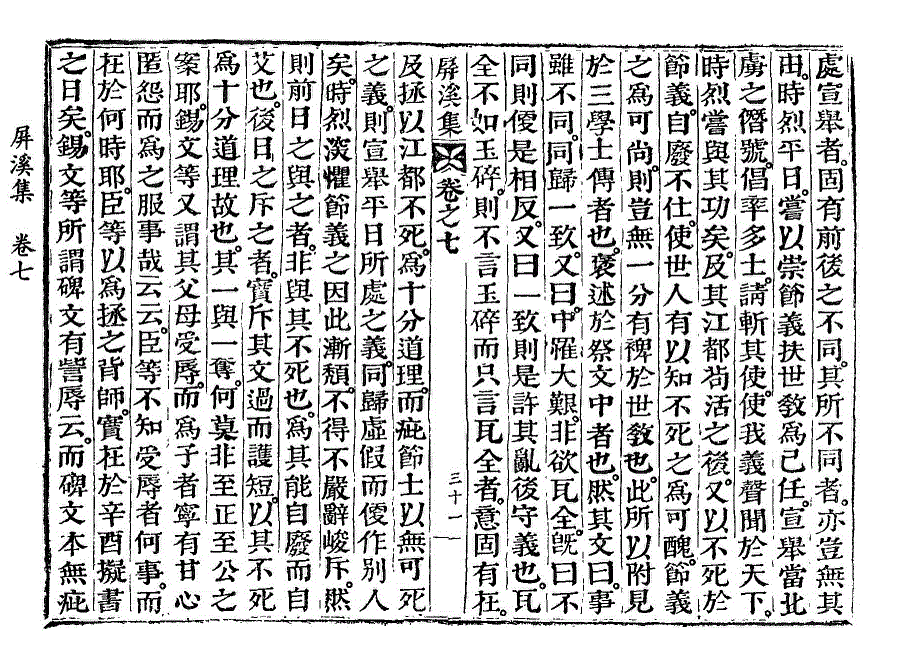 处宣举者。固有前后之不同。其所不同者。亦岂无其由。时烈平日。尝以崇节义扶世教为己任。宣举当北虏之僭号。倡率多士。请斩其使。使我义声闻于天下。时烈尝与其功矣。及其江都苟活之后。又以不死于节义。自废不仕。使世人有以知不死之为可丑。节义之为可尚。则岂无一分有裨于世教也。此所以附见于三学士传者也。褒述于祭文中者也。然其文曰。事虽不同。同归一致。又曰。中罹大艰。非欲瓦全。既曰不同则便是相反。又曰一致则是许其乱后守义也。瓦全不如玉碎。则不言玉碎而只言瓦全者。意固有在。及拯以江都不死。为十分道理。而疵节士以无可死之义。则宣举平日所处之义。同归虚假而便作别人矣。时烈深惧节义之因此渐颓。不得不严辞峻斥。然则前日之与之者。非与其不死也。为其能自废而自艾也。后日之斥之者。实斥其文过而护短。以其不死为十分道理故也。其一与一夺。何莫非至正至公之案耶。锡文等又谓其父母受辱。而为子者宁有甘心匿怨而为之服事哉云云。臣等不知受辱者何事。而在于何时耶。臣等以为拯之背师。实在于辛酉拟书之日矣。锡文等所谓碑文有訾辱云。而碑文本无疵
处宣举者。固有前后之不同。其所不同者。亦岂无其由。时烈平日。尝以崇节义扶世教为己任。宣举当北虏之僭号。倡率多士。请斩其使。使我义声闻于天下。时烈尝与其功矣。及其江都苟活之后。又以不死于节义。自废不仕。使世人有以知不死之为可丑。节义之为可尚。则岂无一分有裨于世教也。此所以附见于三学士传者也。褒述于祭文中者也。然其文曰。事虽不同。同归一致。又曰。中罹大艰。非欲瓦全。既曰不同则便是相反。又曰一致则是许其乱后守义也。瓦全不如玉碎。则不言玉碎而只言瓦全者。意固有在。及拯以江都不死。为十分道理。而疵节士以无可死之义。则宣举平日所处之义。同归虚假而便作别人矣。时烈深惧节义之因此渐颓。不得不严辞峻斥。然则前日之与之者。非与其不死也。为其能自废而自艾也。后日之斥之者。实斥其文过而护短。以其不死为十分道理故也。其一与一夺。何莫非至正至公之案耶。锡文等又谓其父母受辱。而为子者宁有甘心匿怨而为之服事哉云云。臣等不知受辱者何事。而在于何时耶。臣等以为拯之背师。实在于辛酉拟书之日矣。锡文等所谓碑文有訾辱云。而碑文本无疵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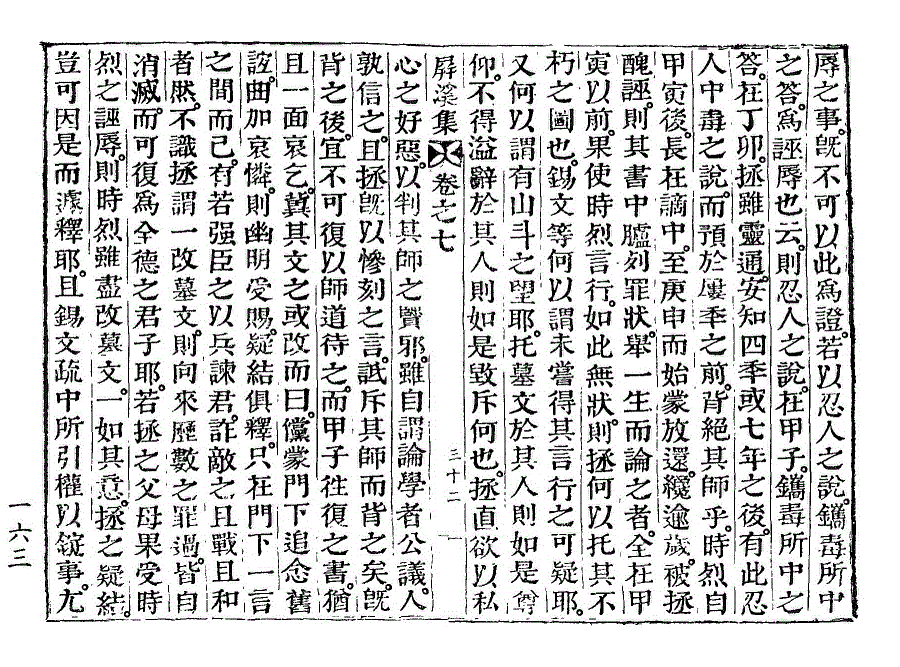 辱之事。既不可以此为證。若以忍人之说。鑴毒所中之答。为诬辱也云。则忍人之说。在甲子。鑴毒所中之答。在丁卯。拯虽灵通。安知四年或七年之后。有此忍人中毒之说。而预于屡年之前。背绝其师乎。时烈自甲寅后。长在谪中。至庚申而始蒙放还。才逾岁。被拯丑诬。则其书中胪列罪状。举一生而论之者。全在甲寅以前。果使时烈言行。如此无状。则拯何以托其不朽之图也。锡文等何以谓未尝得其言行之可疑耶。又何以谓有山斗之望耶。托墓文于其人则如是尊仰。不得溢辞于其人则如是毁斥何也。拯直欲以私心之好恶。以判其师之贤邪。虽自谓论学者公议。人孰信之。且拯既以惨刻之言。诋斥其师而背之矣。既背之后。宜不可复以师道待之。而甲子往复之书。犹且一面哀乞。冀其文之或改而曰。傥蒙门下追念旧谊。曲加哀怜。则幽明受赐。疑结俱释。只在门下一言之间而已。有若强臣之以兵谏君。诈敌之且战且和者然。不识拯谓一改墓文。则向来历数之罪过。皆自消灭。而可复为全德之君子耶。若拯之父母果受时烈之诬辱。则时烈虽尽改墓文。一如其意。拯之疑结。岂可因是而遽释耶。且锡文疏中所引权以锭事。尤
辱之事。既不可以此为證。若以忍人之说。鑴毒所中之答。为诬辱也云。则忍人之说。在甲子。鑴毒所中之答。在丁卯。拯虽灵通。安知四年或七年之后。有此忍人中毒之说。而预于屡年之前。背绝其师乎。时烈自甲寅后。长在谪中。至庚申而始蒙放还。才逾岁。被拯丑诬。则其书中胪列罪状。举一生而论之者。全在甲寅以前。果使时烈言行。如此无状。则拯何以托其不朽之图也。锡文等何以谓未尝得其言行之可疑耶。又何以谓有山斗之望耶。托墓文于其人则如是尊仰。不得溢辞于其人则如是毁斥何也。拯直欲以私心之好恶。以判其师之贤邪。虽自谓论学者公议。人孰信之。且拯既以惨刻之言。诋斥其师而背之矣。既背之后。宜不可复以师道待之。而甲子往复之书。犹且一面哀乞。冀其文之或改而曰。傥蒙门下追念旧谊。曲加哀怜。则幽明受赐。疑结俱释。只在门下一言之间而已。有若强臣之以兵谏君。诈敌之且战且和者然。不识拯谓一改墓文。则向来历数之罪过。皆自消灭。而可复为全德之君子耶。若拯之父母果受时烈之诬辱。则时烈虽尽改墓文。一如其意。拯之疑结。岂可因是而遽释耶。且锡文疏中所引权以锭事。尤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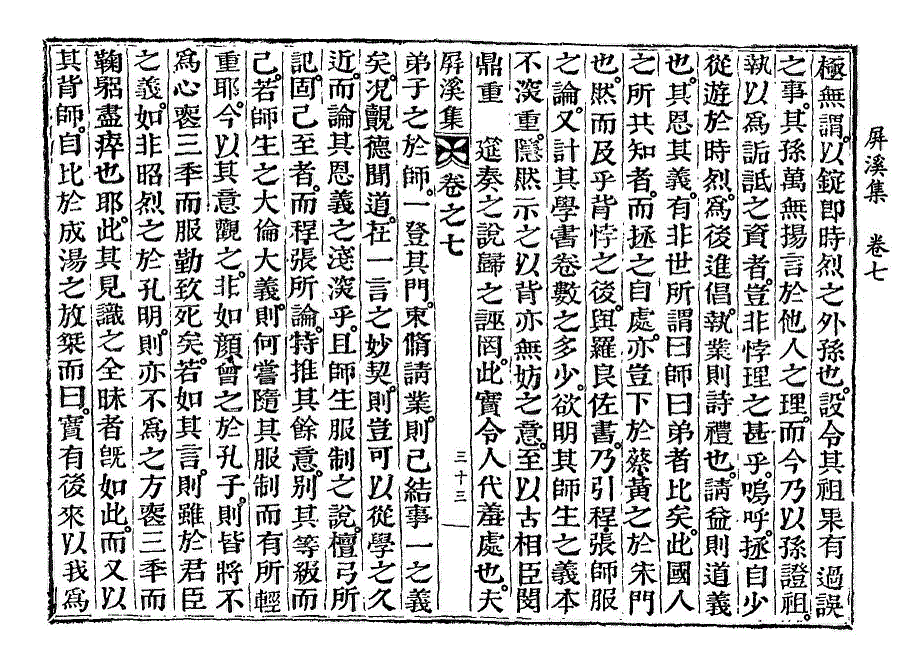 极无谓。以锭即时烈之外孙也。设令其祖果有过误之事。其孙万无扬言于他人之理。而今乃以孙證祖。执以为诟诋之资者。岂非悖理之甚乎。呜呼。拯自少从游于时烈。为后进倡。执业则诗礼也。请益则道义也。其恩其义。有非世所谓曰师曰弟者比矣。此国人之所共知者。而拯之自处。亦岂下于蔡,黄之于朱门也。然而及乎背悖之后。与罗良佐书。乃引程,张师服之论。又计其学书卷数之多少。欲明其师生之义本不深重。隐然示之以背亦无妨之意。至以古相臣闵鼎重 筵奏之说归之诬罔。此实令人代羞处也。夫弟子之于师。一登其门。束脩请业。则已结事一之义矣。况觌德闻道。在一言之妙契。则岂可以从学之久近。而论其恩义之浅深乎。且师生服制之说。檀弓所记。固已至者。而程,张所论。特推其馀意。别其等级而已。若师生之大伦大义。则何尝随其服制而有所轻重耶。今以其意观之。非如颜,曾之于孔子。则皆将不为心丧三年而服勤致死矣。若如其言。则虽于君臣之义。如非昭烈之于孔明。则亦不为之方丧三年而鞠躬尽瘁也耶。此其见识之全昧者既如此。而又以其背师。自比于成汤之放桀而曰。实有后来以我为
极无谓。以锭即时烈之外孙也。设令其祖果有过误之事。其孙万无扬言于他人之理。而今乃以孙證祖。执以为诟诋之资者。岂非悖理之甚乎。呜呼。拯自少从游于时烈。为后进倡。执业则诗礼也。请益则道义也。其恩其义。有非世所谓曰师曰弟者比矣。此国人之所共知者。而拯之自处。亦岂下于蔡,黄之于朱门也。然而及乎背悖之后。与罗良佐书。乃引程,张师服之论。又计其学书卷数之多少。欲明其师生之义本不深重。隐然示之以背亦无妨之意。至以古相臣闵鼎重 筵奏之说归之诬罔。此实令人代羞处也。夫弟子之于师。一登其门。束脩请业。则已结事一之义矣。况觌德闻道。在一言之妙契。则岂可以从学之久近。而论其恩义之浅深乎。且师生服制之说。檀弓所记。固已至者。而程,张所论。特推其馀意。别其等级而已。若师生之大伦大义。则何尝随其服制而有所轻重耶。今以其意观之。非如颜,曾之于孔子。则皆将不为心丧三年而服勤致死矣。若如其言。则虽于君臣之义。如非昭烈之于孔明。则亦不为之方丧三年而鞠躬尽瘁也耶。此其见识之全昧者既如此。而又以其背师。自比于成汤之放桀而曰。实有后来以我为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4L 页
 口实之惭云云。此盖与抵世采书引汤武事。为其攻师之證者。同一语也。其指意之无严。又如此。他何足责哉。锡文等又曰。若曰初何不引义告绝。而函丈门人之称。尚存于乖阻之后。何其畏慎太过。勇决不足也云尔。则先师有灵。必当含笑愧服云。噫。拯之可为愧服于九原之下者。奚特此一事也。锡文等辞穷语屈。为此轻轻容恕之言。其亦可哀也已。锡文等又以时烈祭先正臣金长生文数句语及前祭酒臣权尚夏所撰时烈墓文。或谓之临死怨怼。或谓之绍述为口实云云。噫。拯徒其亦厌闻党鑴之目耶。真所谓操网入海而曰我非渔者也。其果以解人惑耶。此事颠末。既详于前后章疏。今不必架叠。而且以渠所谓辛酉书者观之。其缚束操切。殆与己巳凶徒构杀之启。正相吻合。时烈所谓小子遂有此行。而拯乃骞腾者。只发其微端。尚夏所谓骇机交煽者。亦据实书之。以信来后。而至其拟书出而果大验矣。今以凶徒之启。就校其书。则节节符合。如出一手。而字句之与同。指意之相似处。有不可殚举。虽其辞语互有浅深。而若其构成罪案者。实相表里。今其书始出于世。而与彼凶启一切沕然。抑何故欤。无亦厌然掩藏。曾不肯传
口实之惭云云。此盖与抵世采书引汤武事。为其攻师之證者。同一语也。其指意之无严。又如此。他何足责哉。锡文等又曰。若曰初何不引义告绝。而函丈门人之称。尚存于乖阻之后。何其畏慎太过。勇决不足也云尔。则先师有灵。必当含笑愧服云。噫。拯之可为愧服于九原之下者。奚特此一事也。锡文等辞穷语屈。为此轻轻容恕之言。其亦可哀也已。锡文等又以时烈祭先正臣金长生文数句语及前祭酒臣权尚夏所撰时烈墓文。或谓之临死怨怼。或谓之绍述为口实云云。噫。拯徒其亦厌闻党鑴之目耶。真所谓操网入海而曰我非渔者也。其果以解人惑耶。此事颠末。既详于前后章疏。今不必架叠。而且以渠所谓辛酉书者观之。其缚束操切。殆与己巳凶徒构杀之启。正相吻合。时烈所谓小子遂有此行。而拯乃骞腾者。只发其微端。尚夏所谓骇机交煽者。亦据实书之。以信来后。而至其拟书出而果大验矣。今以凶徒之启。就校其书。则节节符合。如出一手。而字句之与同。指意之相似处。有不可殚举。虽其辞语互有浅深。而若其构成罪案者。实相表里。今其书始出于世。而与彼凶启一切沕然。抑何故欤。无亦厌然掩藏。曾不肯传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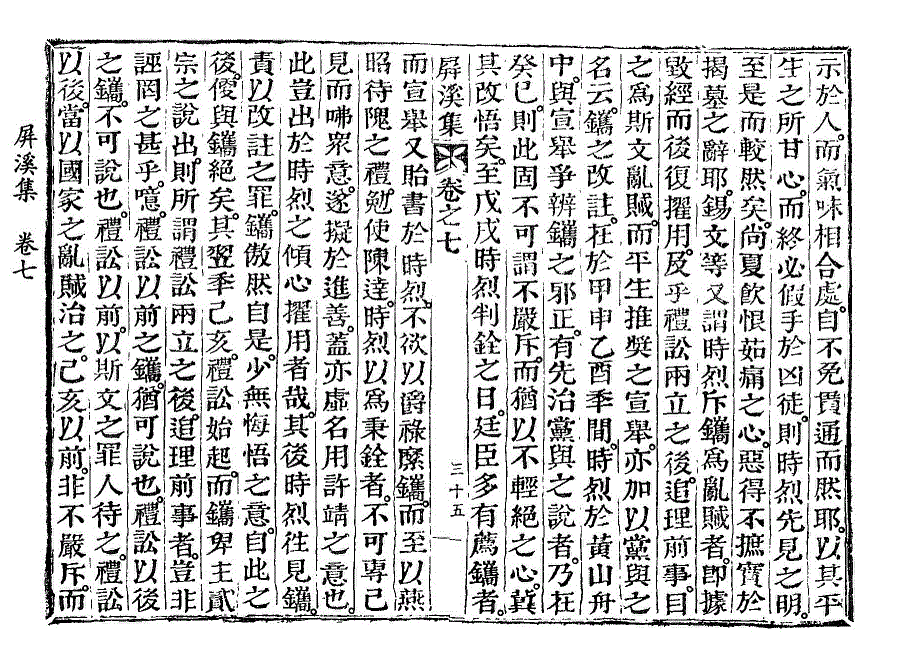 示于人。而气味相合处。自不免贯通而然耶。以其平生之所甘心。而终必假手于凶徒。则时烈先见之明。至是而较然矣。尚夏饮恨茹痛之心。恶得不摭实于揭墓之辞耶。锡文等又谓时烈斥鑴为乱贼者。即据毁经而后复擢用。及乎礼讼两立之后。追理前事。目之为斯文乱贼。而平生推奖之宣举。亦加以党与之名云。鑴之改注。在于甲申乙酉年间。时烈于黄山舟中。与宣举争辨鑴之邪正。有先治党与之说者。乃在癸巳。则此固不可谓不严斥。而犹以不轻绝之心。冀其改悟矣。至戊戌时烈判铨之日。廷臣多有荐鑴者。而宣举又贻书于时烈。不欲以爵禄縻鑴。而至以燕昭待隗之礼。勉使陈达。时烈以为秉铨者。不可专己见而咈众意。遂拟于进善。盖亦虚名用许靖之意也。此岂出于时烈之倾心擢用者哉。其后时烈往见鑴。责以改注之罪。鑴傲然自是。少无悔悟之意。自此之后。便与鑴绝矣。其翌年己亥。礼讼始起。而鑴卑主贰宗之说出。则所谓礼讼两立之后。追理前事者。岂非诬罔之甚乎。噫。礼讼以前之鑴。犹可说也。礼讼以后之鑴。不可说也。礼讼以前。以斯文之罪人待之。礼讼以后。当以国家之乱贼治之。己亥以前。非不严斥。而
示于人。而气味相合处。自不免贯通而然耶。以其平生之所甘心。而终必假手于凶徒。则时烈先见之明。至是而较然矣。尚夏饮恨茹痛之心。恶得不摭实于揭墓之辞耶。锡文等又谓时烈斥鑴为乱贼者。即据毁经而后复擢用。及乎礼讼两立之后。追理前事。目之为斯文乱贼。而平生推奖之宣举。亦加以党与之名云。鑴之改注。在于甲申乙酉年间。时烈于黄山舟中。与宣举争辨鑴之邪正。有先治党与之说者。乃在癸巳。则此固不可谓不严斥。而犹以不轻绝之心。冀其改悟矣。至戊戌时烈判铨之日。廷臣多有荐鑴者。而宣举又贻书于时烈。不欲以爵禄縻鑴。而至以燕昭待隗之礼。勉使陈达。时烈以为秉铨者。不可专己见而咈众意。遂拟于进善。盖亦虚名用许靖之意也。此岂出于时烈之倾心擢用者哉。其后时烈往见鑴。责以改注之罪。鑴傲然自是。少无悔悟之意。自此之后。便与鑴绝矣。其翌年己亥。礼讼始起。而鑴卑主贰宗之说出。则所谓礼讼两立之后。追理前事者。岂非诬罔之甚乎。噫。礼讼以前之鑴。犹可说也。礼讼以后之鑴。不可说也。礼讼以前。以斯文之罪人待之。礼讼以后。当以国家之乱贼治之。己亥以前。非不严斥。而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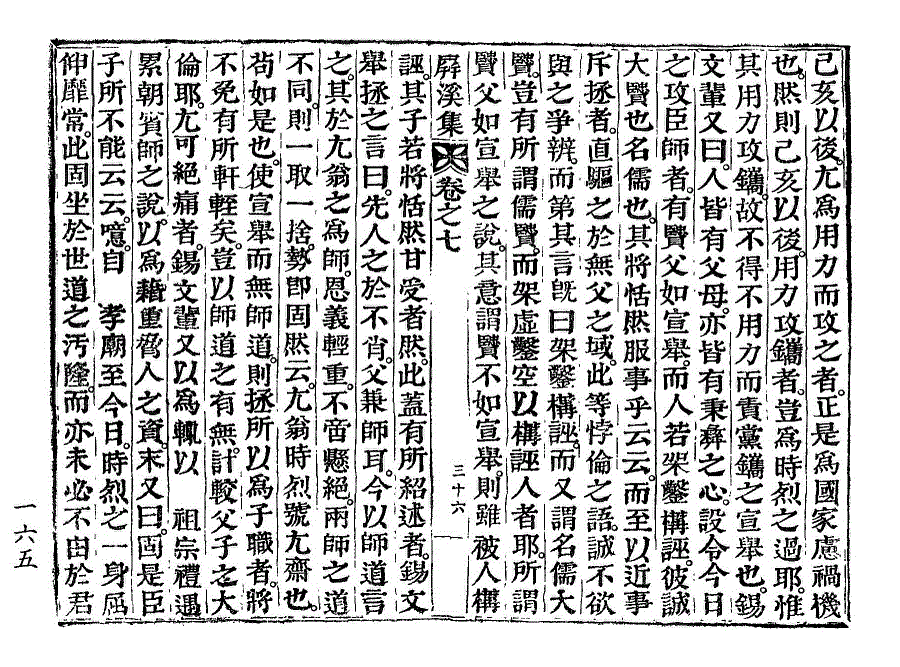 己亥以后。尤为用力而攻之者。正是为国家虑祸机也。然则己亥以后。用力攻鑴者。岂为时烈之过耶。惟其用力攻鑴。故不得不用力而责党鑴之宣举也。锡文辈又曰。人皆有父母。亦皆有秉彝之心。设令今日之攻臣师者。有贤父如宣举。而人若架凿构诬。彼诚大贤也名儒也。其将恬然服事乎云云。而至以近事斥拯者。直驱之于无父之域。此等悖伦之语。诚不欲与之争辨。而第其言既曰架凿构诬。而又谓名儒,大贤。岂有所谓儒贤。而架虚凿空以构诬人者耶。所谓贤父如宣举之说。其意谓贤不如宣举。则虽被人构诬。其子若将恬然甘受者然。此盖有所绍述者。锡文举拯之言曰。先人之于不肖。父兼师耳。今以师道言之。其于尤翁之为师。恩义轻重。不啻悬绝。两师之道不同。则一取一舍。势即固然云。尤翁时烈号尤斋也。苟如是也。使宣举而无师道。则拯所以为子职者。将不免有所轩轾矣。岂以师道之有无。计较父子之大伦耶。尤可绝痛者。锡文辈又以为辄以 祖宗礼遇累朝宾师之说。以为藉重胁人之资。末又曰。固是臣子所不能云云。噫。自 孝庙至今日。时烈之一身屈伸靡常。此固坐于世道之污隆。而亦未必不由于君
己亥以后。尤为用力而攻之者。正是为国家虑祸机也。然则己亥以后。用力攻鑴者。岂为时烈之过耶。惟其用力攻鑴。故不得不用力而责党鑴之宣举也。锡文辈又曰。人皆有父母。亦皆有秉彝之心。设令今日之攻臣师者。有贤父如宣举。而人若架凿构诬。彼诚大贤也名儒也。其将恬然服事乎云云。而至以近事斥拯者。直驱之于无父之域。此等悖伦之语。诚不欲与之争辨。而第其言既曰架凿构诬。而又谓名儒,大贤。岂有所谓儒贤。而架虚凿空以构诬人者耶。所谓贤父如宣举之说。其意谓贤不如宣举。则虽被人构诬。其子若将恬然甘受者然。此盖有所绍述者。锡文举拯之言曰。先人之于不肖。父兼师耳。今以师道言之。其于尤翁之为师。恩义轻重。不啻悬绝。两师之道不同。则一取一舍。势即固然云。尤翁时烈号尤斋也。苟如是也。使宣举而无师道。则拯所以为子职者。将不免有所轩轾矣。岂以师道之有无。计较父子之大伦耶。尤可绝痛者。锡文辈又以为辄以 祖宗礼遇累朝宾师之说。以为藉重胁人之资。末又曰。固是臣子所不能云云。噫。自 孝庙至今日。时烈之一身屈伸靡常。此固坐于世道之污隆。而亦未必不由于君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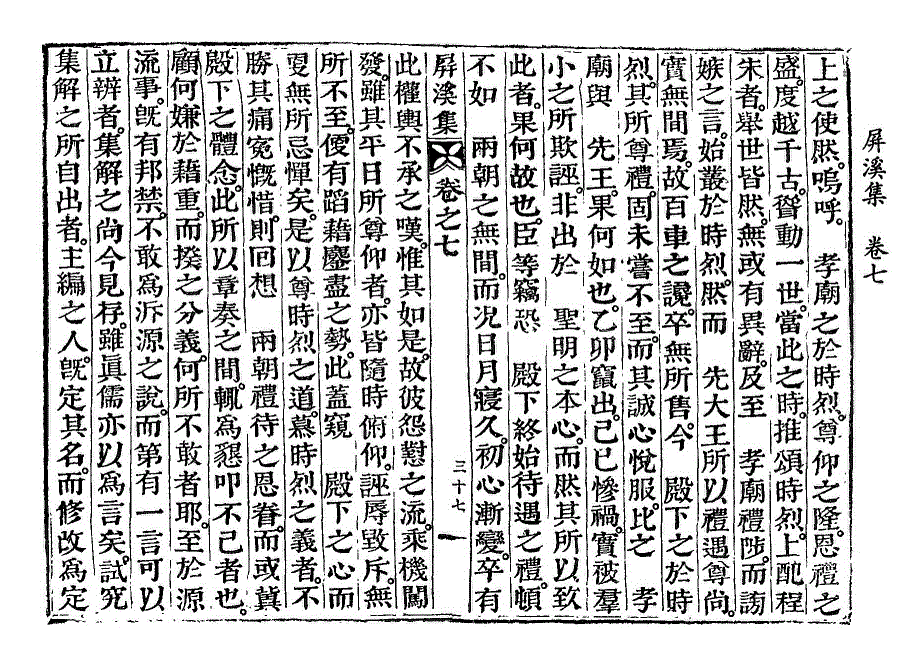 上之使然。呜呼。 孝庙之于时烈。尊仰之隆。恩礼之盛。度越千古。耸动一世。当此之时。推颂时烈。上配程朱者。举世皆然。无或有异辞。及至 孝庙礼陟。而谤嫉之言。始丛于时烈。然而 先大王所以礼遇尊尚。实无间焉。故百车之谗。卒无所售。今 殿下之于时烈。其所尊礼。固未尝不至。而其诚心悦服。比之 孝庙与 先王。果何如也。乙卯窜出。己巳惨祸。实被群小之所欺诬。非出于 圣明之本心。而然其所以致此者。果何故也。臣等窃恐 殿下终始待遇之礼。顿不如 两朝之无间。而况日月寝久。初心渐变。卒有此权舆不承之叹。惟其如是。故彼怨怼之流。乘机闯发。虽其平日所尊仰者。亦皆随时俯仰。诬辱毁斥。无所不至。便有蹈藉鏖尽之势。此盖窥 殿下之心而更无所忌惮矣。是以尊时烈之道。慕时烈之义者。不胜其痛冤慨惜。则回想 两朝礼待之恩眷。而或冀殿下之体念。此所以章奏之间。辄为恳叩不已者也。顾何嫌于藉重。而揆之分义。何所不敢者耶。至于源流事。既有邦禁。不敢为溯源之说。而第有一言可以立辨者。集解之尚今见存。虽真儒亦以为言矣。试究集解之所自出者。主编之人。既定其名。而修改为定
上之使然。呜呼。 孝庙之于时烈。尊仰之隆。恩礼之盛。度越千古。耸动一世。当此之时。推颂时烈。上配程朱者。举世皆然。无或有异辞。及至 孝庙礼陟。而谤嫉之言。始丛于时烈。然而 先大王所以礼遇尊尚。实无间焉。故百车之谗。卒无所售。今 殿下之于时烈。其所尊礼。固未尝不至。而其诚心悦服。比之 孝庙与 先王。果何如也。乙卯窜出。己巳惨祸。实被群小之所欺诬。非出于 圣明之本心。而然其所以致此者。果何故也。臣等窃恐 殿下终始待遇之礼。顿不如 两朝之无间。而况日月寝久。初心渐变。卒有此权舆不承之叹。惟其如是。故彼怨怼之流。乘机闯发。虽其平日所尊仰者。亦皆随时俯仰。诬辱毁斥。无所不至。便有蹈藉鏖尽之势。此盖窥 殿下之心而更无所忌惮矣。是以尊时烈之道。慕时烈之义者。不胜其痛冤慨惜。则回想 两朝礼待之恩眷。而或冀殿下之体念。此所以章奏之间。辄为恳叩不已者也。顾何嫌于藉重。而揆之分义。何所不敢者耶。至于源流事。既有邦禁。不敢为溯源之说。而第有一言可以立辨者。集解之尚今见存。虽真儒亦以为言矣。试究集解之所自出者。主编之人。既定其名。而修改为定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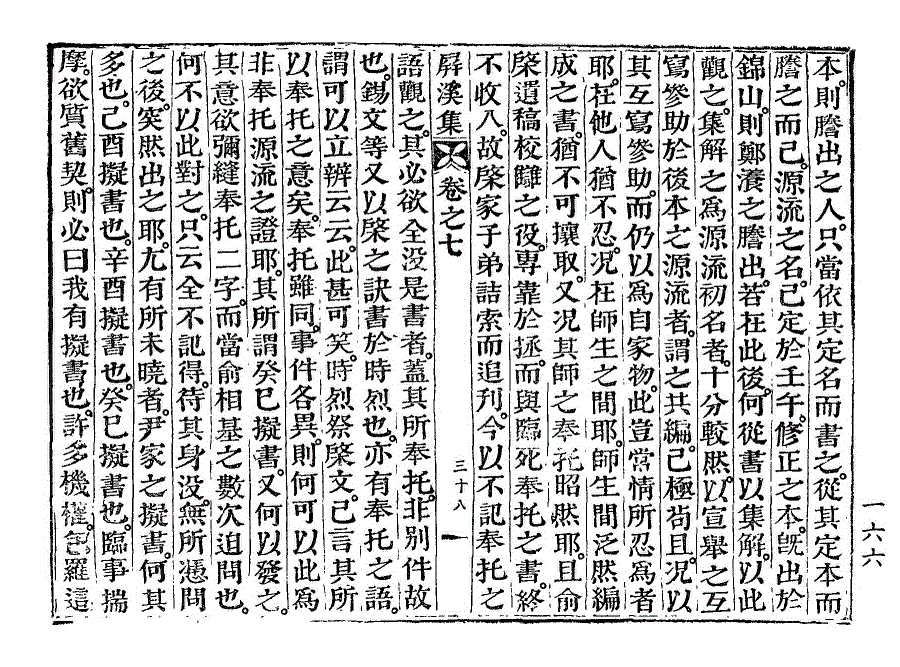 本。则誊出之人。只当依其定名而书之。从其定本而誊之而已。源流之名。已定于壬午。修正之本。既出于锦山。则郑瀁之誊出。若在此后。何从书以集解。以此观之。集解之为源流初名者。十分较然。以宣举之互写参助于后本之源流者。谓之共编。已极苟且。况以其互写参助。而仍以为自家物。此岂常情所忍为者耶。在他人犹不忍。况在师生之间耶。师生间泛然编成之书。犹不可攘取。又况其师之奉托昭然耶。且俞棨遗稿校雠之役。专靠于拯。而与临死奉托之书。终不收入。故棨家子弟诘索而追刊。今以不记奉托之语观之。其必欲全没是书者。盖其所奉托。非别件故也。锡文等又以棨之诀书于时烈也。亦有奉托之语。谓可以立辨云云。此甚可笑。时烈祭棨文。已言其所以奉托之意矣。奉托虽同。事件各异。则何可以此为非奉托源流之證耶。其所谓癸巳拟书。又何以发之。其意欲弥缝奉托二字。而当俞相基之数次迫问也。何不以此对之。只云全不记得。待其身没。无所凭问之后。突然出之耶。尤有所未晓者。尹家之拟书。何其多也。己酉拟书也。辛酉拟书也。癸巳拟书也。临事揣摩。欲质旧契。则必曰我有拟书也。许多机权。包罗这
本。则誊出之人。只当依其定名而书之。从其定本而誊之而已。源流之名。已定于壬午。修正之本。既出于锦山。则郑瀁之誊出。若在此后。何从书以集解。以此观之。集解之为源流初名者。十分较然。以宣举之互写参助于后本之源流者。谓之共编。已极苟且。况以其互写参助。而仍以为自家物。此岂常情所忍为者耶。在他人犹不忍。况在师生之间耶。师生间泛然编成之书。犹不可攘取。又况其师之奉托昭然耶。且俞棨遗稿校雠之役。专靠于拯。而与临死奉托之书。终不收入。故棨家子弟诘索而追刊。今以不记奉托之语观之。其必欲全没是书者。盖其所奉托。非别件故也。锡文等又以棨之诀书于时烈也。亦有奉托之语。谓可以立辨云云。此甚可笑。时烈祭棨文。已言其所以奉托之意矣。奉托虽同。事件各异。则何可以此为非奉托源流之證耶。其所谓癸巳拟书。又何以发之。其意欲弥缝奉托二字。而当俞相基之数次迫问也。何不以此对之。只云全不记得。待其身没。无所凭问之后。突然出之耶。尤有所未晓者。尹家之拟书。何其多也。己酉拟书也。辛酉拟书也。癸巳拟书也。临事揣摩。欲质旧契。则必曰我有拟书也。许多机权。包罗这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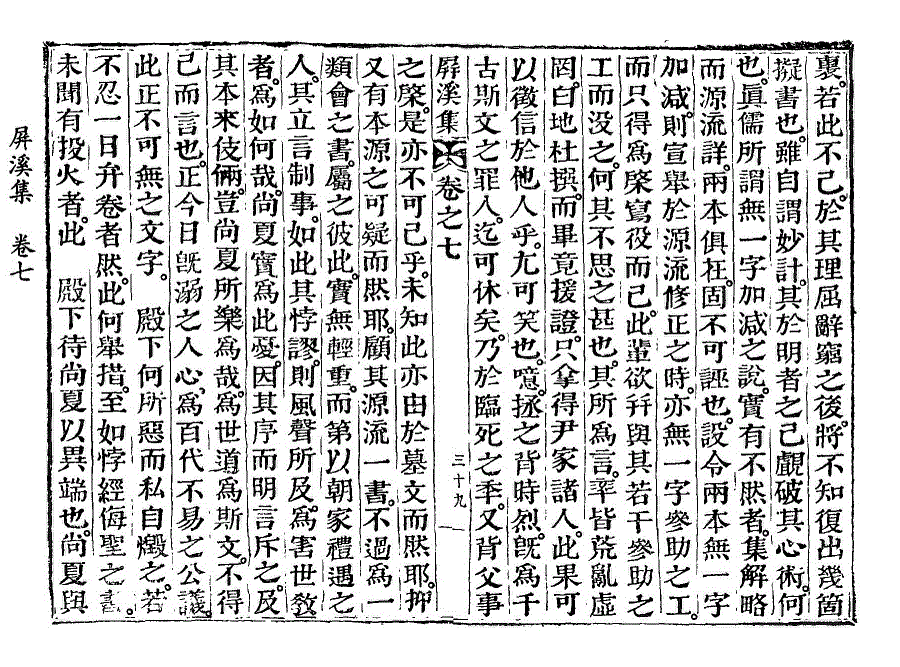 里。若此不已。于其理屈辞穷之后。将不知复出几个拟书也。虽自谓妙计。其于明者之已觑破其心术。何也。真儒所谓无一字加减之说。实有不然者。集解略而源流详。两本俱在。固不可诬也。设令两本无一字加减。则宣举于源流修正之时。亦无一字参助之工。而只得为棨写役而已。此辈欲并与其若干参助之工而没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其所为言。率皆荒乱虚罔。白地杜撰。而毕竟援證。只拿得尹家诸人。此果可以徵信于他人乎。尤可笑也。噫。拯之背时烈。既为千古斯文之罪人。迄可休矣。乃于临死之年。又背父事之棨。是亦不可已乎。未知此亦由于墓文而然耶。抑又有本源之可疑而然耶。顾其源流一书。不过为一类会之书。属之彼此。实无轻重。而第以朝家礼遇之人。其立言制事。如此其悖谬。则风声所及。为害世教者。为如何哉。尚夏实为此忧。因其序而明言斥之。及其本来伎俩。岂尚夏所乐为哉。为世道为斯文。不得已而言也。正今日既溺之人心。为百代不易之公议。此正不可无之文字。 殿下何所恶而私自燬之。若不忍一日弁卷者然。此何举措。至如悖经侮圣之书。未闻有投火者。此 殿下待尚夏以异端也。尚夏与
里。若此不已。于其理屈辞穷之后。将不知复出几个拟书也。虽自谓妙计。其于明者之已觑破其心术。何也。真儒所谓无一字加减之说。实有不然者。集解略而源流详。两本俱在。固不可诬也。设令两本无一字加减。则宣举于源流修正之时。亦无一字参助之工。而只得为棨写役而已。此辈欲并与其若干参助之工而没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其所为言。率皆荒乱虚罔。白地杜撰。而毕竟援證。只拿得尹家诸人。此果可以徵信于他人乎。尤可笑也。噫。拯之背时烈。既为千古斯文之罪人。迄可休矣。乃于临死之年。又背父事之棨。是亦不可已乎。未知此亦由于墓文而然耶。抑又有本源之可疑而然耶。顾其源流一书。不过为一类会之书。属之彼此。实无轻重。而第以朝家礼遇之人。其立言制事。如此其悖谬。则风声所及。为害世教者。为如何哉。尚夏实为此忧。因其序而明言斥之。及其本来伎俩。岂尚夏所乐为哉。为世道为斯文。不得已而言也。正今日既溺之人心。为百代不易之公议。此正不可无之文字。 殿下何所恶而私自燬之。若不忍一日弁卷者然。此何举措。至如悖经侮圣之书。未闻有投火者。此 殿下待尚夏以异端也。尚夏与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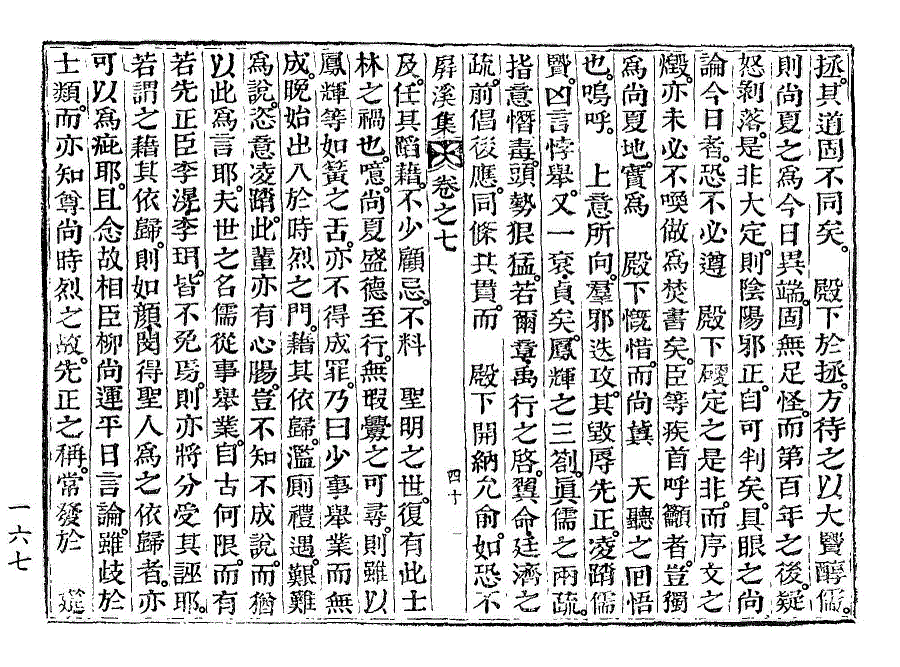 拯。其道固不同矣。 殿下于拯。方待之以大贤醇儒。则尚夏之为今日异端。固无足怪。而第百年之后。疑怒剥落。是非大定。则阴阳邪正。自可判矣。具眼之尚论今日者。恐不必遵 殿下硬定之是非。而序文之燬。亦未必不唤做为焚书矣。臣等疾首呼吁者。岂独为尚夏地。实为 殿下慨惜。而尚冀 天听之回悟也。呜呼。 上意所向。群邪迭攻。其毁辱先正。凌踏儒贤。凶言悖举。又一衮,贞矣。凤辉之三劄。真儒之两疏。指意憯毒。头势狠猛。若尔章,禹行之启。翼命,廷济之疏。前倡后应。同条共贯。而 殿下开纳允俞。如恐不及。任其蹈藉。不少顾忌。不料 圣明之世。复有此士林之祸也。噫。尚夏盛德至行。无瑕衅之可寻。则虽以凤辉等如簧之舌。亦不得成罪。乃曰少事举业而无成。晚始出入于时烈之门。藉其依归。滥厕礼遇。艰难为说。恣意凌踏。此辈亦有心肠。岂不知不成说。而犹以此为言耶。夫世之名儒从事举业。自古何限。而有若先正臣李滉,李珥。皆不免焉。则亦将分受其诬耶。若谓之藉其依归。则如颜,闵得圣人为之依归者。亦可以为疵耶。且念故相臣柳尚运平日言论。虽歧于士类。而亦知尊尚时烈之故。先正之称。常发于 筵
拯。其道固不同矣。 殿下于拯。方待之以大贤醇儒。则尚夏之为今日异端。固无足怪。而第百年之后。疑怒剥落。是非大定。则阴阳邪正。自可判矣。具眼之尚论今日者。恐不必遵 殿下硬定之是非。而序文之燬。亦未必不唤做为焚书矣。臣等疾首呼吁者。岂独为尚夏地。实为 殿下慨惜。而尚冀 天听之回悟也。呜呼。 上意所向。群邪迭攻。其毁辱先正。凌踏儒贤。凶言悖举。又一衮,贞矣。凤辉之三劄。真儒之两疏。指意憯毒。头势狠猛。若尔章,禹行之启。翼命,廷济之疏。前倡后应。同条共贯。而 殿下开纳允俞。如恐不及。任其蹈藉。不少顾忌。不料 圣明之世。复有此士林之祸也。噫。尚夏盛德至行。无瑕衅之可寻。则虽以凤辉等如簧之舌。亦不得成罪。乃曰少事举业而无成。晚始出入于时烈之门。藉其依归。滥厕礼遇。艰难为说。恣意凌踏。此辈亦有心肠。岂不知不成说。而犹以此为言耶。夫世之名儒从事举业。自古何限。而有若先正臣李滉,李珥。皆不免焉。则亦将分受其诬耶。若谓之藉其依归。则如颜,闵得圣人为之依归者。亦可以为疵耶。且念故相臣柳尚运平日言论。虽歧于士类。而亦知尊尚时烈之故。先正之称。常发于 筵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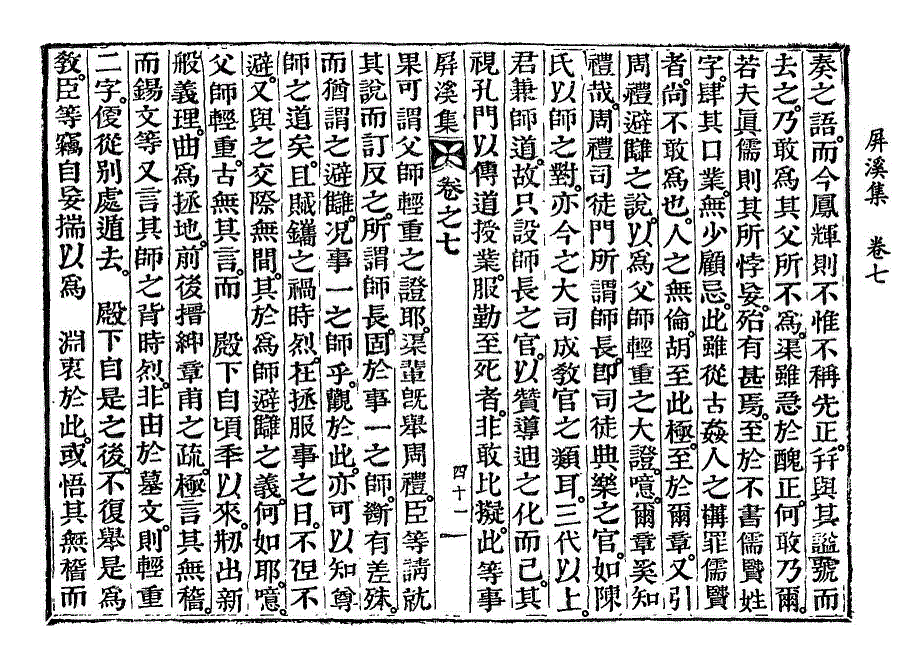 奏之语。而今凤辉则不惟不称先正。并与其谥号而去之。乃敢为其父所不为。渠虽急于丑正。何敢乃尔。若夫真儒则其所悖妄。殆有甚焉。至于不书儒贤姓字。肆其口业。无少顾忌。此虽从古奸人之构罪儒贤者。尚不敢为也。人之无伦。胡至此极。至于尔章。又引周礼避雠之说。以为父师轻重之大證。噫。尔章奚知礼哉。周礼司徒门所谓师长。即司徒典乐之官。如陈氏以师之对。亦今之大司成教官之类耳。三代以上。君兼师道。故只设师长之官。以赞导迪之化而已。其视孔门以传道授业。服勤至死者。非敢比拟。此等事果可谓父师轻重之證耶。渠辈既举周礼。臣等请就其说而订反之。所谓师长。固于事一之师。断有差殊。而犹谓之避雠。况事一之师乎。观于此。亦可以知尊师之道矣。且贼鑴之祸时烈。在拯服事之日。不但不避。又与之交际无间。其于为师避雠之义。何如耶。噫。父师轻重。古无其言。而 殿下自顷年以来。刱出新般义理。曲为拯地。前后搢绅章甫之疏。极言其无稽。而锡文等又言其师之背时烈。非由于墓文。则轻重二字。便从别处遁去。 殿下自是之后。不复举是为教。臣等窃自妄揣以为 渊衷于此。或悟其无稽而
奏之语。而今凤辉则不惟不称先正。并与其谥号而去之。乃敢为其父所不为。渠虽急于丑正。何敢乃尔。若夫真儒则其所悖妄。殆有甚焉。至于不书儒贤姓字。肆其口业。无少顾忌。此虽从古奸人之构罪儒贤者。尚不敢为也。人之无伦。胡至此极。至于尔章。又引周礼避雠之说。以为父师轻重之大證。噫。尔章奚知礼哉。周礼司徒门所谓师长。即司徒典乐之官。如陈氏以师之对。亦今之大司成教官之类耳。三代以上。君兼师道。故只设师长之官。以赞导迪之化而已。其视孔门以传道授业。服勤至死者。非敢比拟。此等事果可谓父师轻重之證耶。渠辈既举周礼。臣等请就其说而订反之。所谓师长。固于事一之师。断有差殊。而犹谓之避雠。况事一之师乎。观于此。亦可以知尊师之道矣。且贼鑴之祸时烈。在拯服事之日。不但不避。又与之交际无间。其于为师避雠之义。何如耶。噫。父师轻重。古无其言。而 殿下自顷年以来。刱出新般义理。曲为拯地。前后搢绅章甫之疏。极言其无稽。而锡文等又言其师之背时烈。非由于墓文。则轻重二字。便从别处遁去。 殿下自是之后。不复举是为教。臣等窃自妄揣以为 渊衷于此。或悟其无稽而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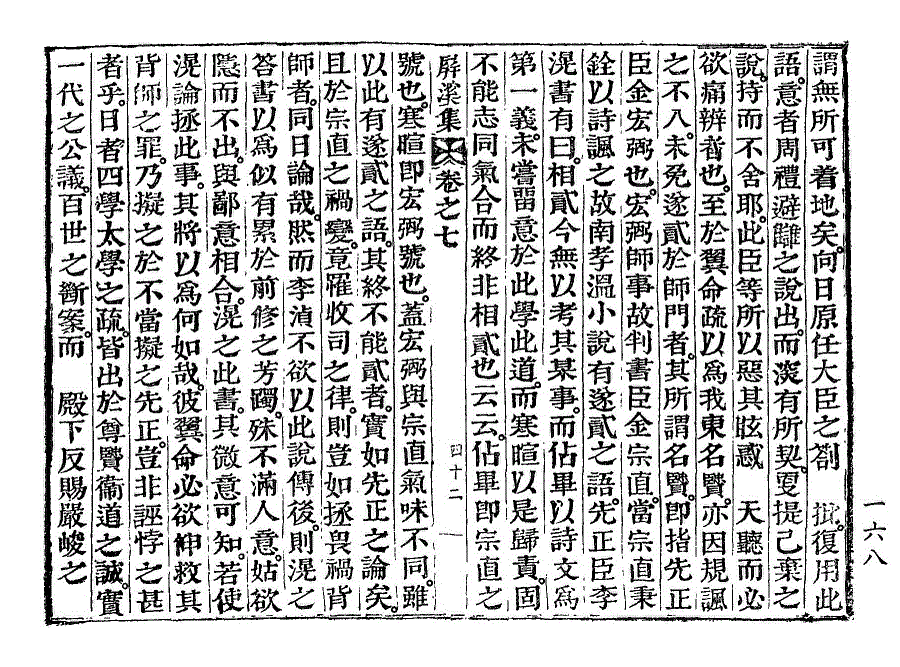 谓无所可着地矣。向日原任大臣之劄 批。复用此语。意者周礼避雠之说出。而深有所契。更提已弃之说。持而不舍耶。此臣等所以恶其眩惑 天听而必欲痛辨者也。至于翼命疏以为我东名贤。亦因规讽之不入。未免遂贰于师门者。其所谓名贤。即指先正臣金宏弼也。宏弼师事故判书臣金宗直。当宗直秉铨以诗讽之故南孝温小说有遂贰之语。先正臣李滉书有曰。相贰今无以考其某事。而佔毕以诗文为第一义。未尝留意于此学此道。而寒暄以是归责。固不能志同气合而终非相贰也云云。佔毕即宗直之号也。寒暄即宏弼号也。盖宏弼与宗直气味不同。虽以此有遂贰之语。其终不能贰者。实如先正之论矣。且于宗直之祸变。竟罹收司之律。则岂如拯畏祸背师者。同日论哉。然而李浈不欲以此说传后。则滉之答书以为似有累于前修之芳躅。殊不满人意。姑欲隐而不出。与鄙意相合。滉之此书。其微意可知。若使滉论拯此事。其将以为何如哉。彼翼命必欲伸救其背师之罪。乃拟之于不当拟之先正。岂非诬悖之甚者乎。日者四学太学之疏。皆出于尊贤卫道之诚。实一代之公议。百世之断案。而 殿下反赐严峻之
谓无所可着地矣。向日原任大臣之劄 批。复用此语。意者周礼避雠之说出。而深有所契。更提已弃之说。持而不舍耶。此臣等所以恶其眩惑 天听而必欲痛辨者也。至于翼命疏以为我东名贤。亦因规讽之不入。未免遂贰于师门者。其所谓名贤。即指先正臣金宏弼也。宏弼师事故判书臣金宗直。当宗直秉铨以诗讽之故南孝温小说有遂贰之语。先正臣李滉书有曰。相贰今无以考其某事。而佔毕以诗文为第一义。未尝留意于此学此道。而寒暄以是归责。固不能志同气合而终非相贰也云云。佔毕即宗直之号也。寒暄即宏弼号也。盖宏弼与宗直气味不同。虽以此有遂贰之语。其终不能贰者。实如先正之论矣。且于宗直之祸变。竟罹收司之律。则岂如拯畏祸背师者。同日论哉。然而李浈不欲以此说传后。则滉之答书以为似有累于前修之芳躅。殊不满人意。姑欲隐而不出。与鄙意相合。滉之此书。其微意可知。若使滉论拯此事。其将以为何如哉。彼翼命必欲伸救其背师之罪。乃拟之于不当拟之先正。岂非诬悖之甚者乎。日者四学太学之疏。皆出于尊贤卫道之诚。实一代之公议。百世之断案。而 殿下反赐严峻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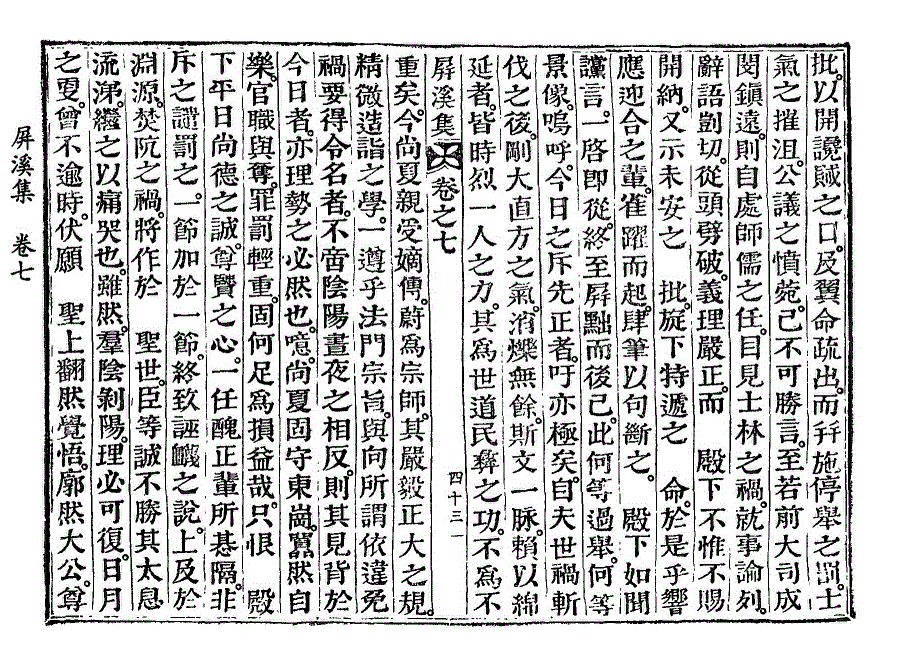 批。以开谗贼之口。及翼命疏出。而并施停举之罚。士气之摧沮。公议之愤菀。已不可胜言。至若前大司成闵镇远。则自处师儒之任。目见士林之祸。就事论列。辞语剀切。从头劈破。义理严正。而 殿下不惟不赐开纳。又示未安之 批。旋下特递之 命。于是乎响应迎合之辈。雀跃而起。肆笔以句断之。 殿下如闻谠言。一启即从。终至屏黜而后已。此何等过举。何等景像。呜呼。今日之斥先正者。吁亦极矣。自夫世祸斩伐之后。刚大直方之气。消烁无馀。斯文一脉。赖以绵延者。皆时烈一人之力。其为世道民彝之功。不为不重矣。今尚夏亲受嫡传。蔚为宗师。其严毅正大之规。精微造诣之学。一遵乎法门宗旨。与向所谓依违免祸要得令名者。不啻阴阳昼夜之相反。则其见背于今日者。亦理势之必然也。噫。尚夏固守东岗。嚣然自乐。官职与夺。罪罚轻重。固何足为损益哉。只恨 殿下平日尚德之诚。尊贤之心。一任丑正辈所惎隔。非斥之谴罚之。一节加于一节。终致诬蔑之说。上及于渊源。焚坑之祸。将作于 圣世。臣等诚不胜其太息流涕。继之以痛哭也。虽然。群阴剥阳。理必可复。日月之更。曾不逾时。伏愿 圣上翻然觉悟。廓然大公。尊
批。以开谗贼之口。及翼命疏出。而并施停举之罚。士气之摧沮。公议之愤菀。已不可胜言。至若前大司成闵镇远。则自处师儒之任。目见士林之祸。就事论列。辞语剀切。从头劈破。义理严正。而 殿下不惟不赐开纳。又示未安之 批。旋下特递之 命。于是乎响应迎合之辈。雀跃而起。肆笔以句断之。 殿下如闻谠言。一启即从。终至屏黜而后已。此何等过举。何等景像。呜呼。今日之斥先正者。吁亦极矣。自夫世祸斩伐之后。刚大直方之气。消烁无馀。斯文一脉。赖以绵延者。皆时烈一人之力。其为世道民彝之功。不为不重矣。今尚夏亲受嫡传。蔚为宗师。其严毅正大之规。精微造诣之学。一遵乎法门宗旨。与向所谓依违免祸要得令名者。不啻阴阳昼夜之相反。则其见背于今日者。亦理势之必然也。噫。尚夏固守东岗。嚣然自乐。官职与夺。罪罚轻重。固何足为损益哉。只恨 殿下平日尚德之诚。尊贤之心。一任丑正辈所惎隔。非斥之谴罚之。一节加于一节。终致诬蔑之说。上及于渊源。焚坑之祸。将作于 圣世。臣等诚不胜其太息流涕。继之以痛哭也。虽然。群阴剥阳。理必可复。日月之更。曾不逾时。伏愿 圣上翻然觉悟。廓然大公。尊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69L 页
 先正之道。念斯文之重。 洞察拯心迹而严斥之。亟收儒臣谴罚而尊礼之。且还师席削黜之 命。仍收疏儒停举之罚。并将前后毒正之辈。快 赐处分。使是非明正。邪正剖判。则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先正之道。念斯文之重。 洞察拯心迹而严斥之。亟收儒臣谴罚而尊礼之。且还师席削黜之 命。仍收疏儒停举之罚。并将前后毒正之辈。快 赐处分。使是非明正。邪正剖判。则斯文幸甚。世道幸甚。代掌令宋思胤请 赐 万东祠祭田。特谥宋公甲祚疏二段。(丁酉)
窃惟先正臣宋时烈当天地翻覆之后。一生以尊周大义。为其家计。常以为环东土数千里。一草一木。莫非 神皇帝再造之恩也。第日月骎久。义理渐晦。世不复知有尊周之义。时烈于晚年。寻常嘅痛。欲就书室之傍。营立祠宇而祭之。庸以寓含忍恻怛之意。亦以明万折必东之义。盖其义则实仿楚人茅屋祭昭王之故事。而朱子亦尝为其友张栻。作南岳庙迎享送神之辞。南岳庙者。虞帝庙也。宗国云亡。血祀既绝。则以编户而祀帝王。可以义起。此先贤所以不以为僭而行之者也。时烈苦心经营。事未就而遽遭己巳之变。遂于耽罗路中。移书于今赞成臣权尚夏。俾卒其志。而辞意丁宁。有足以泣鬼神矣。尚夏既受其师之付托。义不忍孤。乃与若而士友。协谟建宇。至甲申春。始用笾豆之礼。其时 筵臣有以此事白之者。伏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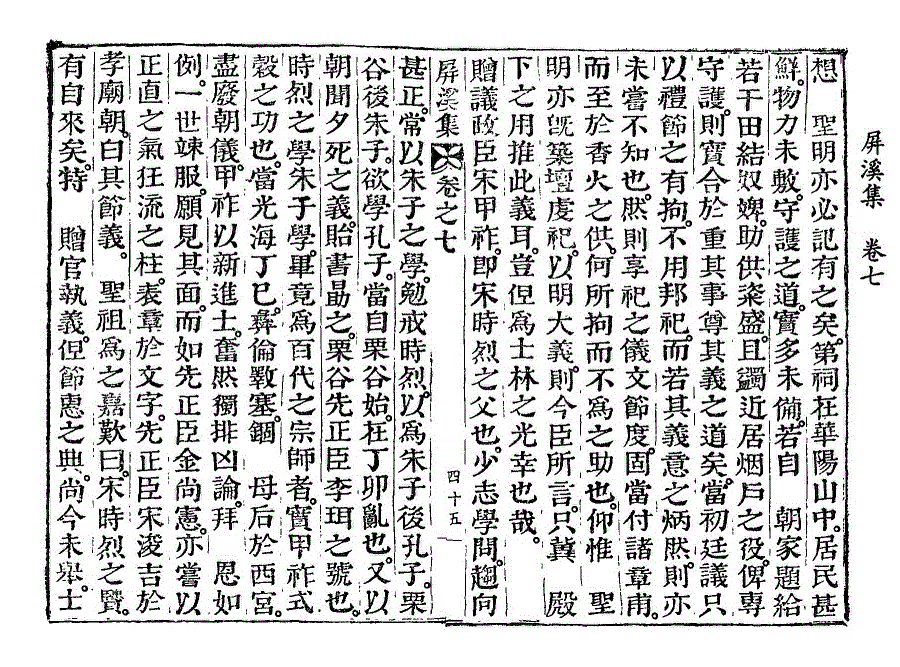 想 圣明亦必记有之矣。第祠在华阳山中。居民甚鲜。物力未敷。守护之道。实多未备。若自 朝家题给若干田结奴婢。助供粢盛。且蠲近居烟户之役。俾专守护。则实合于重其事尊其义之道矣。当初廷议只以礼节之有拘。不用邦祀。而若其义意之炳然。则亦未尝不知也。然则享祀之仪文节度。固当付诸章甫。而至于香火之供。何所拘而不为之助也。仰惟 圣明亦既筑坛虔祀。以明大义。则今臣所言。只冀 殿下之用推此义耳。岂但为士林之光幸也哉。
想 圣明亦必记有之矣。第祠在华阳山中。居民甚鲜。物力未敷。守护之道。实多未备。若自 朝家题给若干田结奴婢。助供粢盛。且蠲近居烟户之役。俾专守护。则实合于重其事尊其义之道矣。当初廷议只以礼节之有拘。不用邦祀。而若其义意之炳然。则亦未尝不知也。然则享祀之仪文节度。固当付诸章甫。而至于香火之供。何所拘而不为之助也。仰惟 圣明亦既筑坛虔祀。以明大义。则今臣所言。只冀 殿下之用推此义耳。岂但为士林之光幸也哉。赠议政臣宋甲祚。即宋时烈之父也。少志学问。趋向甚正。常以朱子之学。勉戒时烈。以为朱子后孔子。栗谷后朱子。欲学孔子。当自栗谷始。在丁卯乱也。又以朝闻夕死之义。贻书勖之。栗谷先正臣李珥之号也。时烈之学朱子学。毕竟为百代之宗师者。实甲祚式谷之功也。当光海丁巳。彝伦斁塞。锢 母后于西宫。尽废朝仪。甲祚以新进士。奋然独排凶论。拜 恩如例。一世竦服。愿见其面。而如先正臣金尚宪。亦尝以正直之气狂流之柱。表章于文字。先正臣宋浚吉于孝庙朝。白其节义。 圣祖为之嘉叹曰。宋时烈之贤。有自来矣。特 赠官执义。但节惠之典。尚今未举。士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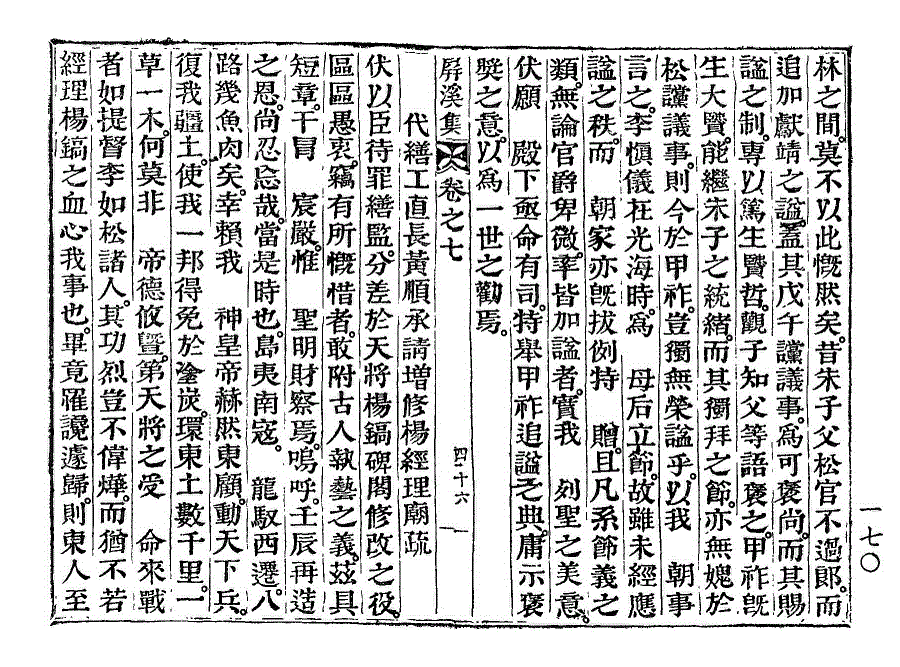 林之间。莫不以此慨然矣。昔朱子父松官不过郎。而追加献靖之谥。盖其戊午谠议事。为可褒尚。而其赐谥之制。专以笃生贤哲。观子知父等语褒之。甲祚既生大贤。能继朱子之统绪。而其独拜之节。亦无愧于松谠议事。则今于甲祚。岂独无荣谥乎。以我 朝事言之。李慎仪在光海时。为 母后立节。故虽未经应谥之秩。而 朝家亦既拔例特 赠。且凡系节义之类。无论官爵卑微。率皆加谥者。实我 列圣之美意。伏愿 殿下亟命有司。特举甲祚追谥之典。庸示褒奖之意。以为一世之劝焉。
林之间。莫不以此慨然矣。昔朱子父松官不过郎。而追加献靖之谥。盖其戊午谠议事。为可褒尚。而其赐谥之制。专以笃生贤哲。观子知父等语褒之。甲祚既生大贤。能继朱子之统绪。而其独拜之节。亦无愧于松谠议事。则今于甲祚。岂独无荣谥乎。以我 朝事言之。李慎仪在光海时。为 母后立节。故虽未经应谥之秩。而 朝家亦既拔例特 赠。且凡系节义之类。无论官爵卑微。率皆加谥者。实我 列圣之美意。伏愿 殿下亟命有司。特举甲祚追谥之典。庸示褒奖之意。以为一世之劝焉。代缮工直长黄顺承请增修杨经理庙疏
伏以臣待罪缮监。分差于天将杨镐碑阁修改之役。区区愚衷。窃有所慨惜者。敢附古人执艺之义。兹具短章。干冒 宸严。惟 圣明财察焉。呜呼。壬辰再造之恩。尚忍忘哉。当是时也。岛夷南寇。 龙驭西迁。八路几鱼肉矣。幸赖我 神皇帝赫然东顾。动天下兵。复我疆土。使我一邦得免于涂炭。环东土数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 帝德攸暨。第天将之受 命来战者如提督李如松诸人。其功烈岂不伟烨。而犹不若经理杨镐之血心我事也。毕竟罹谗遽归。则东人至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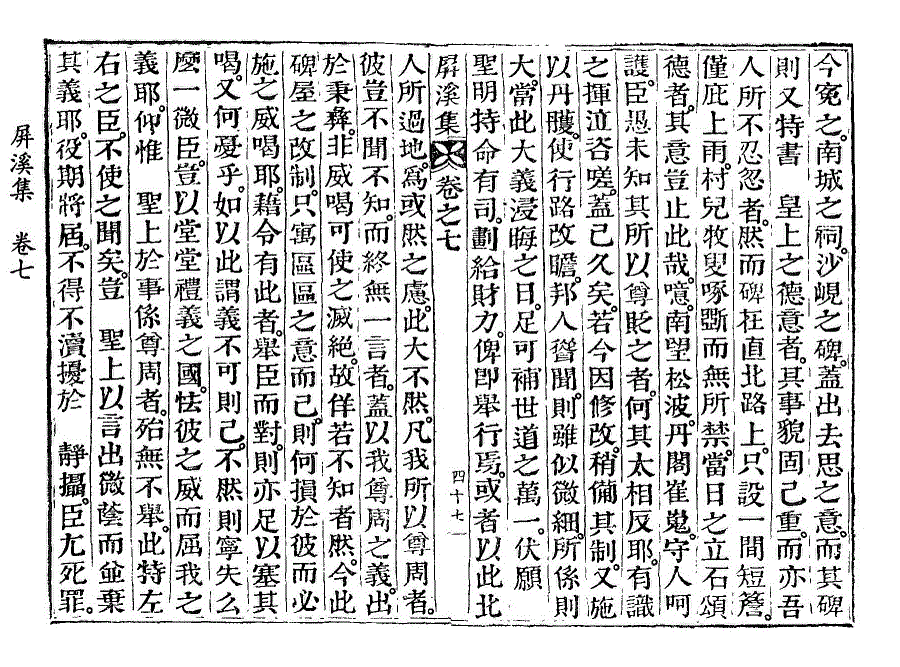 今冤之。南城之祠。沙岘之碑。盖出去思之意。而其碑则又特书 皇上之德意者。其事貌固已重。而亦吾人所不忍忽者。然而碑在直北路上。只设一间短檐。仅庇上雨。村儿牧叟啄斲而无所禁。当日之立石颂德者。其意岂止此哉。噫。南望松波。丹阁崔嵬。守人呵护。臣愚未知其所以尊贬之者。何其太相反耶。有识之挥泣咨嗟。盖已久矣。若今因修改。稍备其制。又施以丹雘。使行路改瞻。邦人耸闻。则虽似微细。所系则大。当此大义浸晦之日。足可补世道之万一。伏愿 圣明特命有司。划给财力。俾即举行焉。或者以此北人所过地。为或然之虑。此大不然。凡我所以尊周者。彼岂不闻不知。而终无一言者。盖以我尊周之义。出于秉彝。非威喝可使之灭绝。故佯若不知者然。今此碑屋之改制。只寓区区之意而已。则何损于彼而必施之威喝耶。藉令有此者。举臣而对。则亦足以塞其喝。又何忧乎。如以此谓义不可则已。不然则宁失幺么一微臣。岂以堂堂礼义之国。怯彼之威而屈我之义耶。仰惟 圣上于事系尊周者。殆无不举。此特左右之臣。不使之闻矣。岂 圣上以言出微荫而并弃其义耶。役期将届。不得不渎扰于 静摄。臣尤死罪。
今冤之。南城之祠。沙岘之碑。盖出去思之意。而其碑则又特书 皇上之德意者。其事貌固已重。而亦吾人所不忍忽者。然而碑在直北路上。只设一间短檐。仅庇上雨。村儿牧叟啄斲而无所禁。当日之立石颂德者。其意岂止此哉。噫。南望松波。丹阁崔嵬。守人呵护。臣愚未知其所以尊贬之者。何其太相反耶。有识之挥泣咨嗟。盖已久矣。若今因修改。稍备其制。又施以丹雘。使行路改瞻。邦人耸闻。则虽似微细。所系则大。当此大义浸晦之日。足可补世道之万一。伏愿 圣明特命有司。划给财力。俾即举行焉。或者以此北人所过地。为或然之虑。此大不然。凡我所以尊周者。彼岂不闻不知。而终无一言者。盖以我尊周之义。出于秉彝。非威喝可使之灭绝。故佯若不知者然。今此碑屋之改制。只寓区区之意而已。则何损于彼而必施之威喝耶。藉令有此者。举臣而对。则亦足以塞其喝。又何忧乎。如以此谓义不可则已。不然则宁失幺么一微臣。岂以堂堂礼义之国。怯彼之威而屈我之义耶。仰惟 圣上于事系尊周者。殆无不举。此特左右之臣。不使之闻矣。岂 圣上以言出微荫而并弃其义耶。役期将届。不得不渎扰于 静摄。臣尤死罪。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1L 页
 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门生疏(甲辰○疏头李蓍圣。卞致云诬辱。累呈政院。终不得捧入。)
伏以臣等亡师先正臣权尚夏养德山林。矜式一世。嫡承乎先儒之统。宗师乎后学之士。 先朝之所礼遇也。 圣明之所尊敬也。臣等愚昧蔑裂。百无肖似。而盖尝出入函丈之间。蒙被罔极之恩。恶言御侮。虽愧圣门之勇。三生一事。亦闻先哲之训矣。不幸士林无禄。梁木遽摧。伥伥迷道。永失依仰。而况自数年以来。百怪蜿蜒。师道燬败。一脉斯文。无地可寄。臣等只宜抱书穷林。杜门枯死。以为守先师之道。报先师之恩者。庶其在此矣。顷年台臣论窜金砺而搀及臣师。语极悖谬。臣等冤酷痛骇。殆无以自立。而只得退守无辨之戒。不敢为伸㬥之举者。谅出于不获已也。乃者斯文之祸愈憯。丑正之论迭发。至有申致云者闯居言地。首先攘臂。请削臣师之职。一启再启。去益阴凶。臣等得见其所谓启辞。则句句言言。萃合捏造。罔非驱之于恶逆之地。读未中半。百体震掉。毛发皆竖。噫嘻痛哉。此何人也。此何言也。臣等旋窃思之。范祖禹于伊川。非纯师也。当伊川之被诬。祖禹不即辨理。则朱子犹且讥之。况臣等之于尚夏。相视如父子。且
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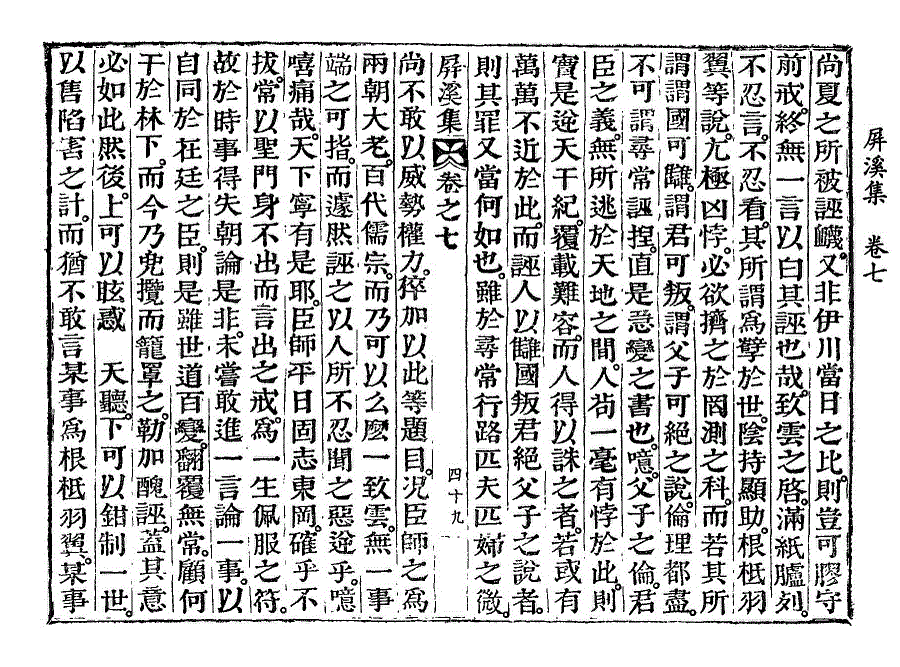 尚夏之所被诬蔑。又非伊川当日之比。则岂可胶守前戒。终无一言以白其诬也哉。致云之启。满纸胪列。不忍言。不忍看。其所谓为孽于世。阴持显助。根柢羽翼等说。尤极凶悖。必欲挤之于罔测之科。而若其所谓谓国可雠。谓君可叛。谓父子可绝之说。伦理都尽。不可谓寻常诬捏。直是急变之书也。噫。父子之伦。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苟一毫有悖于此。则实是逆天干纪。覆载难容。而人得以诛之者。若或有万万不近于此。而诬人以雠国叛君绝父子之说者。则其罪又当何如也。虽于寻常行路匹夫匹妇之微。尚不敢以威势权力。猝加以此等题目。况臣师之为两朝大老。百代儒宗。而乃可以幺么一致云。无一事端之可指。而遽然诬之以人所不忍闻之恶逆乎。噫嘻痛哉。天下宁有是耶。臣师平日固志东冈。确乎不拔。常以圣门身不出而言出之戒。为一生佩服之符。故于时事得失朝论是非。未尝敢进一言论一事。以自同于在廷之臣。则是虽世道百变。翻覆无常。顾何干于林下。而今乃兜揽而笼罩之。勒加丑诬。盖其意必如此然后。上可以眩惑 天听。下可以钳制一世。以售陷害之计。而犹不敢言某事为根柢羽翼。某事
尚夏之所被诬蔑。又非伊川当日之比。则岂可胶守前戒。终无一言以白其诬也哉。致云之启。满纸胪列。不忍言。不忍看。其所谓为孽于世。阴持显助。根柢羽翼等说。尤极凶悖。必欲挤之于罔测之科。而若其所谓谓国可雠。谓君可叛。谓父子可绝之说。伦理都尽。不可谓寻常诬捏。直是急变之书也。噫。父子之伦。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苟一毫有悖于此。则实是逆天干纪。覆载难容。而人得以诛之者。若或有万万不近于此。而诬人以雠国叛君绝父子之说者。则其罪又当何如也。虽于寻常行路匹夫匹妇之微。尚不敢以威势权力。猝加以此等题目。况臣师之为两朝大老。百代儒宗。而乃可以幺么一致云。无一事端之可指。而遽然诬之以人所不忍闻之恶逆乎。噫嘻痛哉。天下宁有是耶。臣师平日固志东冈。确乎不拔。常以圣门身不出而言出之戒。为一生佩服之符。故于时事得失朝论是非。未尝敢进一言论一事。以自同于在廷之臣。则是虽世道百变。翻覆无常。顾何干于林下。而今乃兜揽而笼罩之。勒加丑诬。盖其意必如此然后。上可以眩惑 天听。下可以钳制一世。以售陷害之计。而犹不敢言某事为根柢羽翼。某事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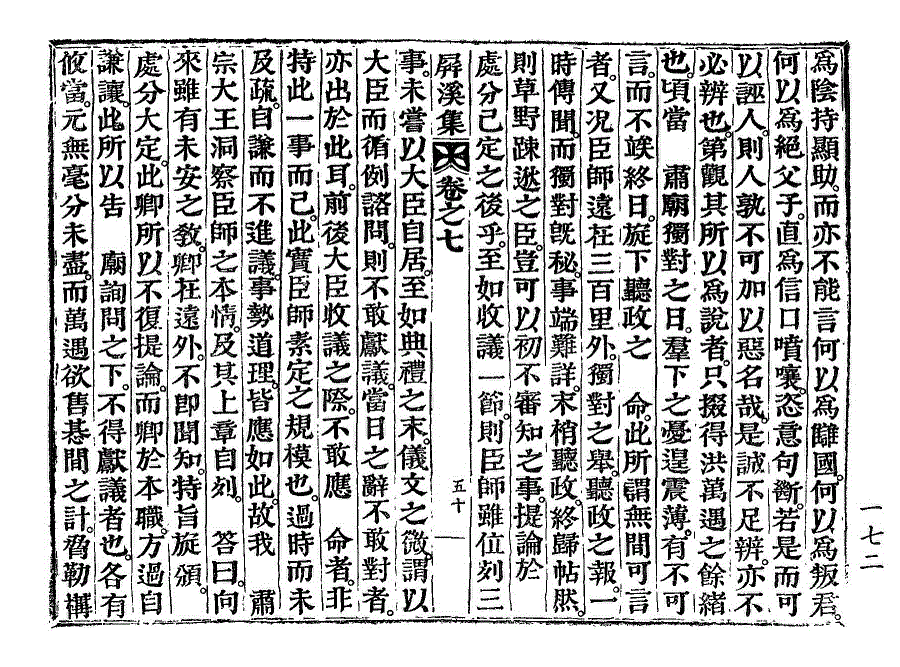 为阴持显助。而亦不能言何以为雠国。何以为叛君。何以为绝父子。直为信口喷嚷。恣意句断。若是而可以诬人。则人孰不可加以恶名哉。是诚不足辨。亦不必辨也。第观其所以为说者。只掇得洪万遇之馀绪也。顷当 肃庙独对之日。群下之忧遑震薄。有不可言。而不俟终日。旋下听政之 命。此所谓无间可言者。又况臣师远在三百里外。独对之举。听政之报。一时传闻。而独对既秘。事端难详。末梢听政。终归帖然。则草野疏逖之臣。岂可以初不审知之事。提论于 处分已定之后乎。至如收议一节。则臣师虽位列三事。未尝以大臣自居。至如典礼之末。仪文之微。谓以大臣而循例咨问。则不敢献议。当日之辞不敢对者。亦出于此耳。前后大臣收议之际。不敢应 命者。非特此一事而已。此实臣师素定之规模也。过时而未及疏。自谦而不进议。事势道理。皆应如此。故我 肃宗大王洞察臣师之本情。及其上章自列。 答曰。向来虽有未安之教。卿在远外。不即闻知。特旨旋颁。 处分大定。此卿所以不复提论。而卿于本职。方过自谦让。此所以告 庙询问之下。不得献议者也。各有攸当。元无毫分未尽。而万遇欲售惎间之计。胁勒构
为阴持显助。而亦不能言何以为雠国。何以为叛君。何以为绝父子。直为信口喷嚷。恣意句断。若是而可以诬人。则人孰不可加以恶名哉。是诚不足辨。亦不必辨也。第观其所以为说者。只掇得洪万遇之馀绪也。顷当 肃庙独对之日。群下之忧遑震薄。有不可言。而不俟终日。旋下听政之 命。此所谓无间可言者。又况臣师远在三百里外。独对之举。听政之报。一时传闻。而独对既秘。事端难详。末梢听政。终归帖然。则草野疏逖之臣。岂可以初不审知之事。提论于 处分已定之后乎。至如收议一节。则臣师虽位列三事。未尝以大臣自居。至如典礼之末。仪文之微。谓以大臣而循例咨问。则不敢献议。当日之辞不敢对者。亦出于此耳。前后大臣收议之际。不敢应 命者。非特此一事而已。此实臣师素定之规模也。过时而未及疏。自谦而不进议。事势道理。皆应如此。故我 肃宗大王洞察臣师之本情。及其上章自列。 答曰。向来虽有未安之教。卿在远外。不即闻知。特旨旋颁。 处分大定。此卿所以不复提论。而卿于本职。方过自谦让。此所以告 庙询问之下。不得献议者也。各有攸当。元无毫分未尽。而万遇欲售惎间之计。胁勒构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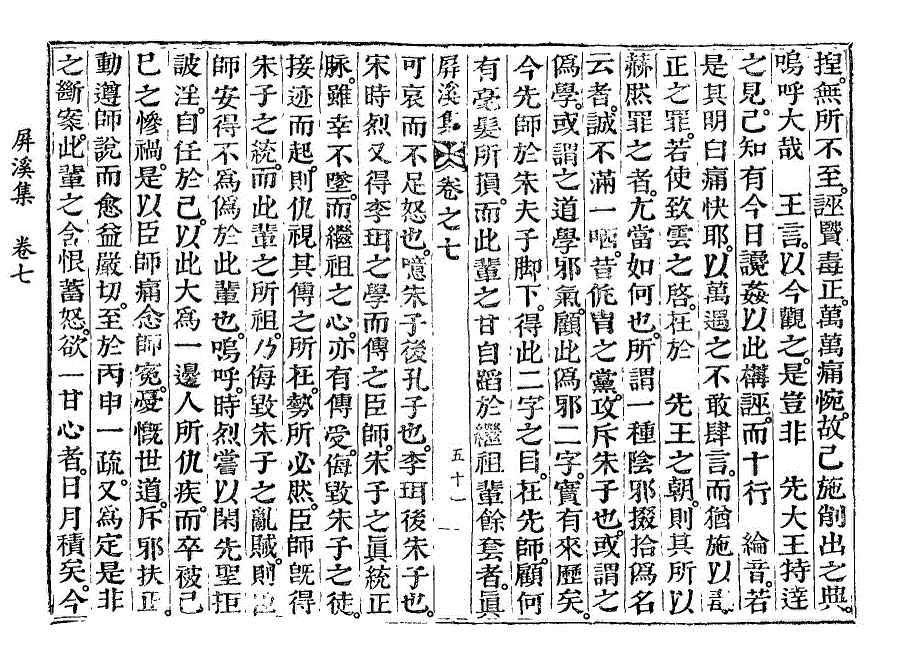 捏。无所不至。诬贤毒正。万万痛惋。故已施削出之典。呜呼大哉 王言。以今观之。是岂非 先大王特达之见。已知有今日谗奸以此构诬。而十行 纶音。若是其明白痛快耶。以万遇之不敢肆言。而犹施以毒正之罪。若使致云之启。在于 先王之朝。则其所以赫然罪之者。尤当如何也。所谓一种阴邪掇拾伪名云者。诚不满一哂。昔侂胄之党。攻斥朱子也。或谓之伪学。或谓之道学邪气。顾此伪邪二字。实有来历矣。今先师于朱夫子脚下。得此二字之目。在先师。顾何有毫发所损。而此辈之甘自蹈于继祖辈馀套者。真可哀而不足怒也。噫朱子后孔子也。李珥后朱子也。宋时烈又得李珥之学而传之臣师。朱子之真统正脉。虽幸不坠。而继祖之心。亦有传受。侮毁朱子之徒。接迹而起。则仇视其传之所在。势所必然。臣师既得朱子之统。而此辈之所祖。乃侮毁朱子之乱贼。则臣师安得不为伪于此辈也。呜呼。时烈尝以闲先圣拒诐淫。自任于己。以此大为一边人所仇疾。而卒被己巳之惨祸。是以臣师痛念师冤。忧慨世道。斥邪扶正。动遵师说而愈益严切。至于丙申一疏。又为定是非之断案。此辈之含恨蓄怒。欲一甘心者。日月积矣。今
捏。无所不至。诬贤毒正。万万痛惋。故已施削出之典。呜呼大哉 王言。以今观之。是岂非 先大王特达之见。已知有今日谗奸以此构诬。而十行 纶音。若是其明白痛快耶。以万遇之不敢肆言。而犹施以毒正之罪。若使致云之启。在于 先王之朝。则其所以赫然罪之者。尤当如何也。所谓一种阴邪掇拾伪名云者。诚不满一哂。昔侂胄之党。攻斥朱子也。或谓之伪学。或谓之道学邪气。顾此伪邪二字。实有来历矣。今先师于朱夫子脚下。得此二字之目。在先师。顾何有毫发所损。而此辈之甘自蹈于继祖辈馀套者。真可哀而不足怒也。噫朱子后孔子也。李珥后朱子也。宋时烈又得李珥之学而传之臣师。朱子之真统正脉。虽幸不坠。而继祖之心。亦有传受。侮毁朱子之徒。接迹而起。则仇视其传之所在。势所必然。臣师既得朱子之统。而此辈之所祖。乃侮毁朱子之乱贼。则臣师安得不为伪于此辈也。呜呼。时烈尝以闲先圣拒诐淫。自任于己。以此大为一边人所仇疾。而卒被己巳之惨祸。是以臣师痛念师冤。忧慨世道。斥邪扶正。动遵师说而愈益严切。至于丙申一疏。又为定是非之断案。此辈之含恨蓄怒。欲一甘心者。日月积矣。今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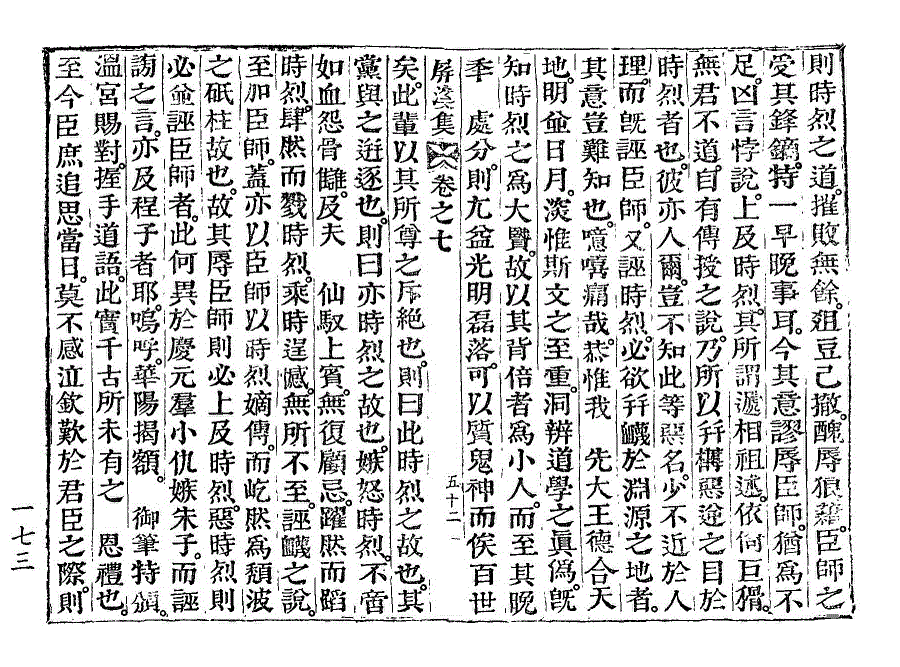 则时烈之道。摧败无馀。俎豆已撤。丑辱狼藉。臣师之受其锋镝。特一早晚事耳。今其意谬辱臣师。犹为不足。凶言悖说。上及时烈。其所谓递相祖述。依倚巨猾。无君不道。自有传授之说。乃所以并构恶逆之目于时烈者也。彼亦人尔。岂不知此等恶名。少不近于人理。而既诬臣师。又诬时烈。必欲并蔑于渊源之地者。其意岂难知也。噫嘻痛哉。恭惟我 先大王德合天地。明并日月。深惟斯文之至重。洞辨道学之真伪。既知时烈之为大贤。故以其背倍者为小人。而至其晚年 处分。则尤益光明磊落。可以质鬼神而俟百世矣。此辈以其所尊之斥绝也。则曰此时烈之故也。其党与之迸逐也。则曰亦时烈之故也。嫉怒时烈。不啻如血怨骨雠。及夫 仙驭上宾。无复顾忌。跃然而蹈时烈。肆然而戮时烈。乘时逞憾。无所不至。诬蔑之说。至加臣师。盖亦以臣师以时烈嫡传。而屹然为颓波之砥柱故也。故其辱臣师则必上及时烈。恶时烈则必并诬臣师者。此何异于庆元群小仇嫉朱子。而诬谤之言。亦及程子者耶。呜呼。华阳揭额。 御笔特颁。温宫赐对。握手道语。此实千古所未有之 恩礼也。至今臣庶追思当日。莫不感泣钦叹于君臣之际。则
则时烈之道。摧败无馀。俎豆已撤。丑辱狼藉。臣师之受其锋镝。特一早晚事耳。今其意谬辱臣师。犹为不足。凶言悖说。上及时烈。其所谓递相祖述。依倚巨猾。无君不道。自有传授之说。乃所以并构恶逆之目于时烈者也。彼亦人尔。岂不知此等恶名。少不近于人理。而既诬臣师。又诬时烈。必欲并蔑于渊源之地者。其意岂难知也。噫嘻痛哉。恭惟我 先大王德合天地。明并日月。深惟斯文之至重。洞辨道学之真伪。既知时烈之为大贤。故以其背倍者为小人。而至其晚年 处分。则尤益光明磊落。可以质鬼神而俟百世矣。此辈以其所尊之斥绝也。则曰此时烈之故也。其党与之迸逐也。则曰亦时烈之故也。嫉怒时烈。不啻如血怨骨雠。及夫 仙驭上宾。无复顾忌。跃然而蹈时烈。肆然而戮时烈。乘时逞憾。无所不至。诬蔑之说。至加臣师。盖亦以臣师以时烈嫡传。而屹然为颓波之砥柱故也。故其辱臣师则必上及时烈。恶时烈则必并诬臣师者。此何异于庆元群小仇嫉朱子。而诬谤之言。亦及程子者耶。呜呼。华阳揭额。 御笔特颁。温宫赐对。握手道语。此实千古所未有之 恩礼也。至今臣庶追思当日。莫不感泣钦叹于君臣之际。则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4H 页
 此辈夫孰非 先王臣子。而乃于没世不忘之日。蹈藉两臣。构陷两臣。略无忌惮。噫。今日廷臣。莫非致云而仇视贤人。肆诬逞毒。致云为甚者。盖有由矣。古语不云乎。不见其山。见其草木。背君附贼。灭绝伦常而世济其凶。大为士类之所罪斥者。既非别人。则彼以其遗种馀孽。乘机跳踉。以快私忿。无足怪也。至如赵镇禧之演出致云之口气。益肆无伦之悖说者。其死党毒正之习。固亦此辈之本色。而所可恨者。以 殿下善继先志之孝。独不念 先大王事关斯文。顾不重欤之教耶。丁宁付托。可泣鬼神。而曾未几何。该曹请黜时烈之院享。则无一辞而可之。致云请夺尚夏之官爵。则又二启而即 允之。不少留难。如受谠言。臣等未敢知。 先王批中斯文之重者。果指何人。而殿下所以处二臣者。乃至于此耶。如二臣者道德不足为斯文之标准。黜陟不得为世道之污隆。则授受大事也。所可言者何限。而必以此并与精一心法而明告而申戒之哉。呜呼。臣等此言。非敢藉 先朝之旧事。故陈于 殿下之前也。 殿下亦尝言 先朝眷遇臣师之意矣。当 殿下代理之日。臣师方在师傅之列。 殿下所以尊礼臣师者。一视诸 大朝处
此辈夫孰非 先王臣子。而乃于没世不忘之日。蹈藉两臣。构陷两臣。略无忌惮。噫。今日廷臣。莫非致云而仇视贤人。肆诬逞毒。致云为甚者。盖有由矣。古语不云乎。不见其山。见其草木。背君附贼。灭绝伦常而世济其凶。大为士类之所罪斥者。既非别人。则彼以其遗种馀孽。乘机跳踉。以快私忿。无足怪也。至如赵镇禧之演出致云之口气。益肆无伦之悖说者。其死党毒正之习。固亦此辈之本色。而所可恨者。以 殿下善继先志之孝。独不念 先大王事关斯文。顾不重欤之教耶。丁宁付托。可泣鬼神。而曾未几何。该曹请黜时烈之院享。则无一辞而可之。致云请夺尚夏之官爵。则又二启而即 允之。不少留难。如受谠言。臣等未敢知。 先王批中斯文之重者。果指何人。而殿下所以处二臣者。乃至于此耶。如二臣者道德不足为斯文之标准。黜陟不得为世道之污隆。则授受大事也。所可言者何限。而必以此并与精一心法而明告而申戒之哉。呜呼。臣等此言。非敢藉 先朝之旧事。故陈于 殿下之前也。 殿下亦尝言 先朝眷遇臣师之意矣。当 殿下代理之日。臣师方在师傅之列。 殿下所以尊礼臣师者。一视诸 大朝处屏溪先生集卷之七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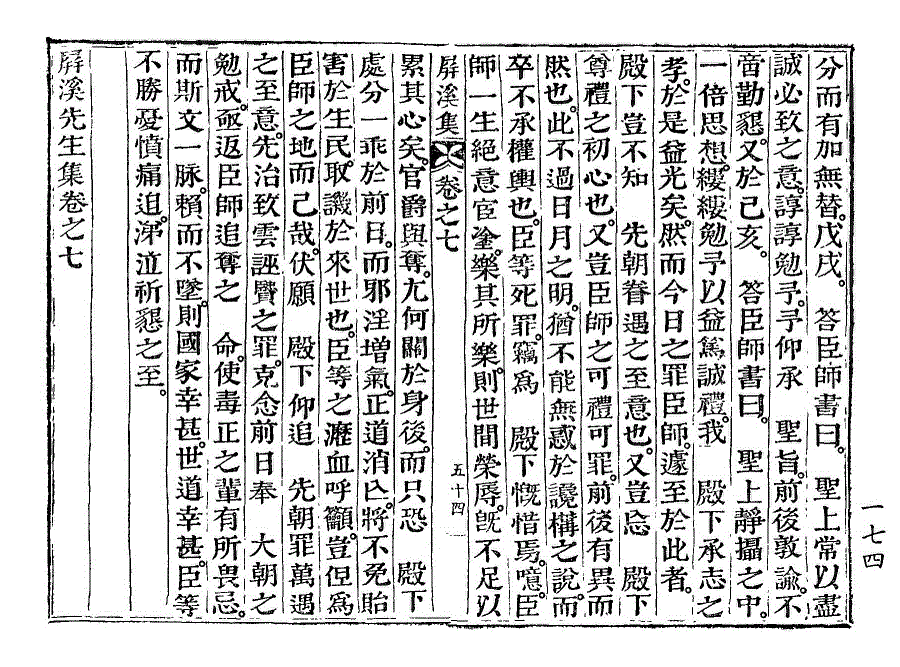 分而有加无替。戊戌。 答臣师书曰。 圣上常以尽诚必致之意。谆谆勉予。予仰承 圣旨。前后敦谕。不啻勤恳。又于己亥。 答臣师书曰。 圣上静摄之中。一倍思想。缕缕勉予以益笃诚礼。我 殿下承志之孝。于是益光矣。然而今日之罪臣师。遽至于此者。 殿下岂不知 先朝眷遇之至意也。又岂忘 殿下尊礼之初心也。又岂臣师之可礼可罪。前后有异而然也。此不过日月之明。犹不能无惑于谗构之说。而卒不承权舆也。臣等死罪。窃为 殿下慨惜焉。噫。臣师一生绝意宦涂。乐其所乐。则世间荣辱。既不足以累其心矣。官爵与夺。尤何关于身后。而只恐 殿下处分一乖于前日。而邪淫增气。正道消亡。将不免贻害于生民。取讥于来世也。臣等之沥血呼吁。岂但为臣师之地而已哉。伏愿 殿下仰追 先朝罪万遇之至意。先治致云诬贤之罪。克念前日奉 大朝之勉戒。亟返臣师追夺之 命。使毒正之辈有所畏忌。而斯文一脉。赖而不坠。则国家幸甚。世道幸甚。臣等不胜忧愤痛迫。涕泣祈恳之至。
分而有加无替。戊戌。 答臣师书曰。 圣上常以尽诚必致之意。谆谆勉予。予仰承 圣旨。前后敦谕。不啻勤恳。又于己亥。 答臣师书曰。 圣上静摄之中。一倍思想。缕缕勉予以益笃诚礼。我 殿下承志之孝。于是益光矣。然而今日之罪臣师。遽至于此者。 殿下岂不知 先朝眷遇之至意也。又岂忘 殿下尊礼之初心也。又岂臣师之可礼可罪。前后有异而然也。此不过日月之明。犹不能无惑于谗构之说。而卒不承权舆也。臣等死罪。窃为 殿下慨惜焉。噫。臣师一生绝意宦涂。乐其所乐。则世间荣辱。既不足以累其心矣。官爵与夺。尤何关于身后。而只恐 殿下处分一乖于前日。而邪淫增气。正道消亡。将不免贻害于生民。取讥于来世也。臣等之沥血呼吁。岂但为臣师之地而已哉。伏愿 殿下仰追 先朝罪万遇之至意。先治致云诬贤之罪。克念前日奉 大朝之勉戒。亟返臣师追夺之 命。使毒正之辈有所畏忌。而斯文一脉。赖而不坠。则国家幸甚。世道幸甚。臣等不胜忧愤痛迫。涕泣祈恳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