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x 页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书
书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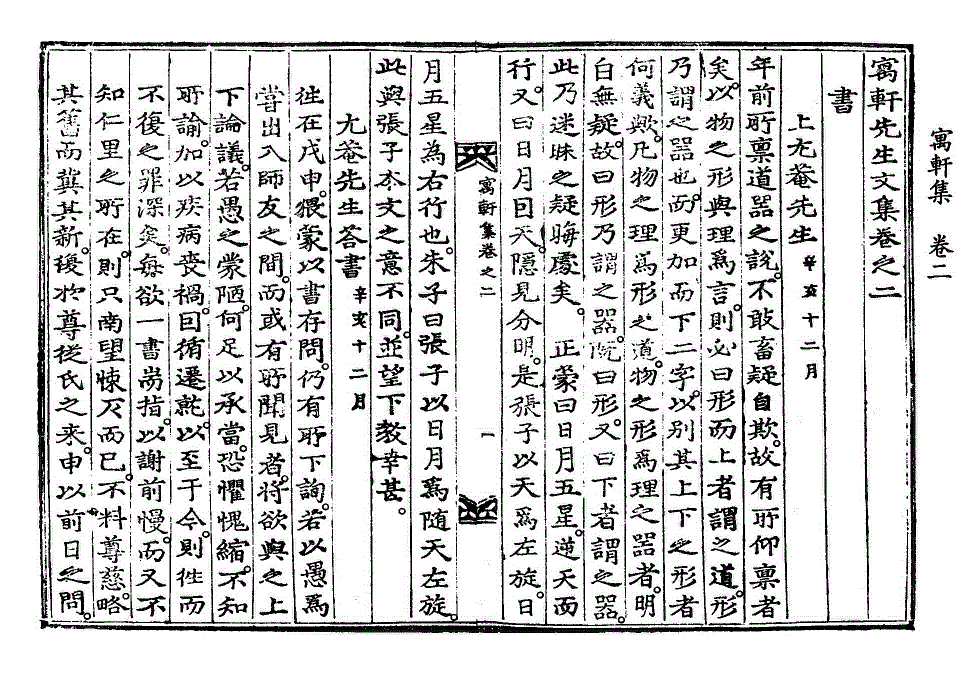 上尤庵先生(辛亥十二月)
上尤庵先生(辛亥十二月)年前所禀道器之说。不敢畜疑自欺。故有所仰禀者矣。以物之形与理为言。则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乃谓之器也。而更加而下二字。以别其上下之形者何义欤。凡物之理为形之道。物之形为理之器者。明白无疑。故曰形乃谓之器。既曰形。又曰下者谓之器。此乃迷昧之疑晦处矣。 正蒙曰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又曰日月因天。隐见分明。是张子以天为左旋。日月五星为右行也。朱子曰张子以日月为随天左旋。此与张子本文之意不同。并望下教幸甚。
尤庵先生答书(辛亥十二月)
往在戊申。猥蒙以书存问。仍有所下询。若以愚为尝出入师友之间。而或有所闻见者。将欲与之上下论议。若愚之蒙陋。何足以承当。恐惧愧缩。不知所谕。加以疾病丧祸。因循迁就。以至于今。则往而不复之罪深矣。每欲一书耑指。以谢前慢。而又不知仁里之所在。则只南望悚仄而已。不料尊慈。略其旧而冀其新。复于尊从氏之来。申以前日之问。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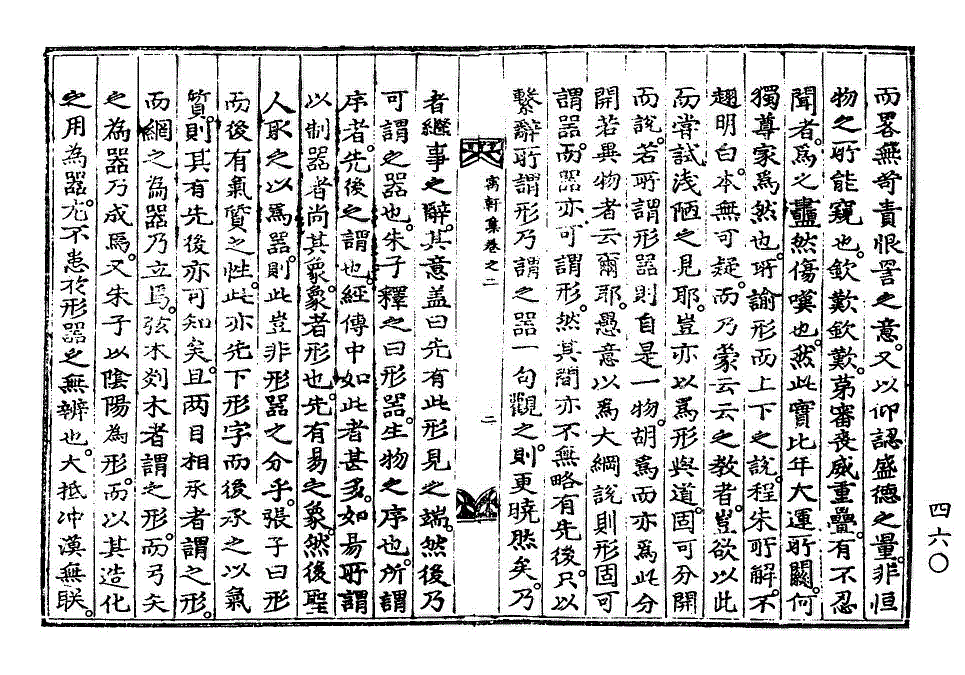 而略无苛责恨詈之意。又以仰认盛德之量。非恒物之所能窥也。钦叹钦叹。第审丧威重叠。有不忍闻者。为之衋然伤叹也。然此实比年大运所关。何独尊家为然也。所谕形而上下之说。程朱所解。不趐明白。本无可疑。而乃蒙云云之教者。岂欲以此而尝试浅陋之见耶。岂亦以为形与道。固可分开而说。若所谓形器则自是一物。胡为而亦为此分开若异物者云尔耶。愚意以为大纲说则形固可谓器。而器亦可谓形。然其间亦不无略有先后。只以系辞所谓形乃谓之器一句观之。则更晓然矣。乃者继事之辞。其意盖曰先有此形见之端。然后乃可谓之器也。朱子释之曰形器。生物之序也。所谓序者。先后之谓也。经传中如此者甚多。如易所谓以制器者尚其象。象者形也。先有易之象。然后圣人取之以为器。则此岂非形器之分乎。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此亦先下形字而后承之以气质。则其有先后亦可知矣。且两目相承者谓之形。而网之为器乃立焉。弦木剡木者谓之形。而弓矢之为器乃成焉。又朱子以阴阳为形。而以其造化之用为器。尤不患于形器之无辨也。大抵冲漠无眹。
而略无苛责恨詈之意。又以仰认盛德之量。非恒物之所能窥也。钦叹钦叹。第审丧威重叠。有不忍闻者。为之衋然伤叹也。然此实比年大运所关。何独尊家为然也。所谕形而上下之说。程朱所解。不趐明白。本无可疑。而乃蒙云云之教者。岂欲以此而尝试浅陋之见耶。岂亦以为形与道。固可分开而说。若所谓形器则自是一物。胡为而亦为此分开若异物者云尔耶。愚意以为大纲说则形固可谓器。而器亦可谓形。然其间亦不无略有先后。只以系辞所谓形乃谓之器一句观之。则更晓然矣。乃者继事之辞。其意盖曰先有此形见之端。然后乃可谓之器也。朱子释之曰形器。生物之序也。所谓序者。先后之谓也。经传中如此者甚多。如易所谓以制器者尚其象。象者形也。先有易之象。然后圣人取之以为器。则此岂非形器之分乎。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此亦先下形字而后承之以气质。则其有先后亦可知矣。且两目相承者谓之形。而网之为器乃立焉。弦木剡木者谓之形。而弓矢之为器乃成焉。又朱子以阴阳为形。而以其造化之用为器。尤不患于形器之无辨也。大抵冲漠无眹。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1H 页
 万象森然已具。则形已具于道中。而犹着而上二字则其于形器而着而下二字。又何疑乎。愚见如此。未知信否。若日月五星之运。谓之左旋可也。谓之右旋亦可也。然张子尝曰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小迟则反右矣。所谓顺之者。谓亦左旋也。何尝专以为右旋如来谕之云乎。若指其反右者而言。则虽谓之右旋亦可也。故朱子注尧典则以日月左旋为说。而至解诗之十月之交。则又以为右行。言各有所当矣。此等处。恐不须执一论也。如何如何。前日所投少册子。当时固爱玩无已。欲俟他日一一还禀。而以为求教之地矣。及归乡里。亟检行笥而无见焉。岂其时苍黄去国之际。遗失于京邸耶。不敏之咎。于是为甚矣。幸乞宽其诛而复以见示。俾得毕其愚。而受益于切磋之际。如何如何。大病之馀。神思脱落。前日所闻。十忘八九。而又院便大忙。不能尽所怀。惟高明谅察焉。
万象森然已具。则形已具于道中。而犹着而上二字则其于形器而着而下二字。又何疑乎。愚见如此。未知信否。若日月五星之运。谓之左旋可也。谓之右旋亦可也。然张子尝曰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小迟则反右矣。所谓顺之者。谓亦左旋也。何尝专以为右旋如来谕之云乎。若指其反右者而言。则虽谓之右旋亦可也。故朱子注尧典则以日月左旋为说。而至解诗之十月之交。则又以为右行。言各有所当矣。此等处。恐不须执一论也。如何如何。前日所投少册子。当时固爱玩无已。欲俟他日一一还禀。而以为求教之地矣。及归乡里。亟检行笥而无见焉。岂其时苍黄去国之际。遗失于京邸耶。不敏之咎。于是为甚矣。幸乞宽其诛而复以见示。俾得毕其愚。而受益于切磋之际。如何如何。大病之馀。神思脱落。前日所闻。十忘八九。而又院便大忙。不能尽所怀。惟高明谅察焉。上尤庵先生(癸丑二月)
壬子春。谨承 下复书。伏蒙不鄙。教告详悉。始知大君子诲人不倦之盛德也。且感且幸。无以为谢。日月五星之运。既闻 命矣。不必更烦。而但张子所谓天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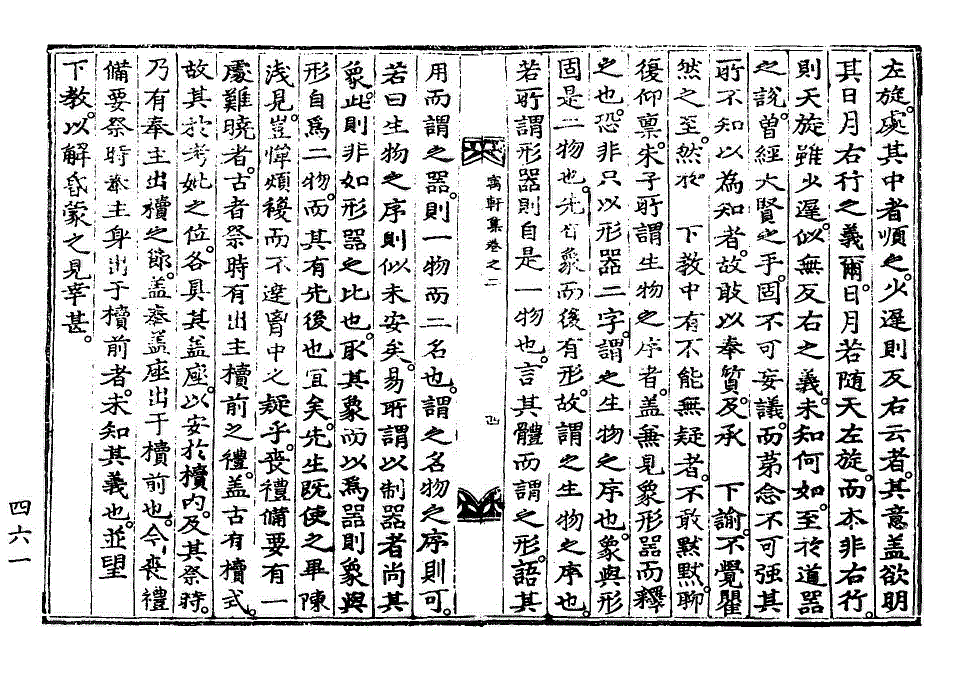 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云者。其意盖欲明其日月右行之义尔。日月若随天左旋。而本非右行。则天旋虽少迟。似无反右之义。未知何如。至于道器之说。曾经大贤之手。固不可妄议。而第念不可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敢以奉质。及承 下谕。不觉瞿然之至。然于 下教中有不能无疑者。不敢默默。聊复仰禀。朱子所谓生物之序者。盖兼见象形器而释之也。恐非只以形器二字。谓之生物之序也。象与形固是二物也。先有象而后有形。故谓之生物之序也。若所谓形器则自是一物也。言其体而谓之形。语其用而谓之器。则一物而二名也。谓之名物之序则可。若曰生物之序则似未安矣。易所谓以制器者尚其象。此则非如形器之比也。取其象而以为器则象与形自为二物。而其有先后也宜矣。先生既使之毕陈浅见。岂惮烦复而不达胸中之疑乎。丧礼备要有一处难晓者。古者祭时有出主椟前之礼。盖古有椟式。故其于考妣之位。各具其盖座。以安于椟内。及其祭时。乃有奉主出椟之节。盖奉盖座出于椟前也。今丧礼备要祭时奉主身出于椟前者。未知其义也。并望 下教。以解昏蒙之见幸甚。
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云者。其意盖欲明其日月右行之义尔。日月若随天左旋。而本非右行。则天旋虽少迟。似无反右之义。未知何如。至于道器之说。曾经大贤之手。固不可妄议。而第念不可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敢以奉质。及承 下谕。不觉瞿然之至。然于 下教中有不能无疑者。不敢默默。聊复仰禀。朱子所谓生物之序者。盖兼见象形器而释之也。恐非只以形器二字。谓之生物之序也。象与形固是二物也。先有象而后有形。故谓之生物之序也。若所谓形器则自是一物也。言其体而谓之形。语其用而谓之器。则一物而二名也。谓之名物之序则可。若曰生物之序则似未安矣。易所谓以制器者尚其象。此则非如形器之比也。取其象而以为器则象与形自为二物。而其有先后也宜矣。先生既使之毕陈浅见。岂惮烦复而不达胸中之疑乎。丧礼备要有一处难晓者。古者祭时有出主椟前之礼。盖古有椟式。故其于考妣之位。各具其盖座。以安于椟内。及其祭时。乃有奉主出椟之节。盖奉盖座出于椟前也。今丧礼备要祭时奉主身出于椟前者。未知其义也。并望 下教。以解昏蒙之见幸甚。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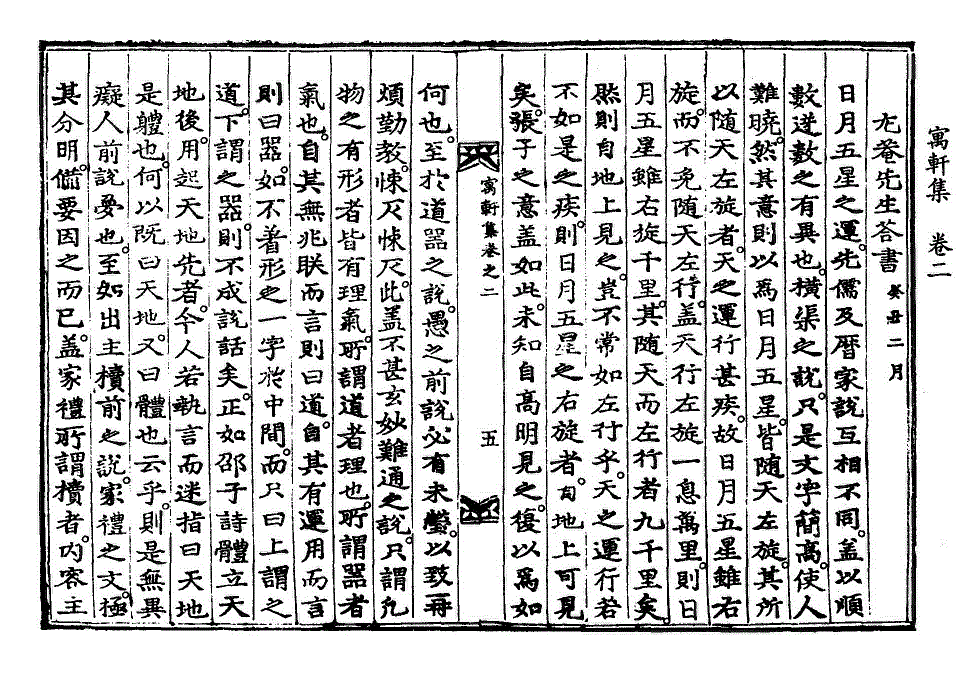 尤庵先生答书(癸丑二月)
尤庵先生答书(癸丑二月)日月五星之运。先儒及历家说互相不同。盖以顺数逆数之有异也。横渠之说。只是文字简高。使人难晓。然其意则以为日月五星。皆随天左旋。其所以随天左旋者。天之运行甚疾。故日月五星虽右旋。而不免随天左行。盖天行左旋一息万里。则日月五星虽右旋千里。其随天而左行者九千里矣。然则自地上见之。岂不常如左行乎。天之运行若不如是之疾。则日月五星之右旋者。自地上可见矣。张子之意盖如此。未知自高明见之。复以为如何也。至于道器之说。愚之前说必有未莹。以致再烦勤教。悚仄悚仄。此盖不甚玄妙难通之说。只谓凡物之有形者皆有理气。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自其无兆眹而言则曰道。自其有运用而言则曰器。如不着形之一字于中间。而只曰上谓之道。下谓之器。则不成说话矣。正如邵子诗体立天地后。用起天地先者。今人若执言而迷指曰天地是体也。何以既曰天地。又曰体也云乎。则是无异痴人前说梦也。至如出主椟前之说。家礼之文。极其分明。备要因之而已。盖家礼所谓椟者。内容主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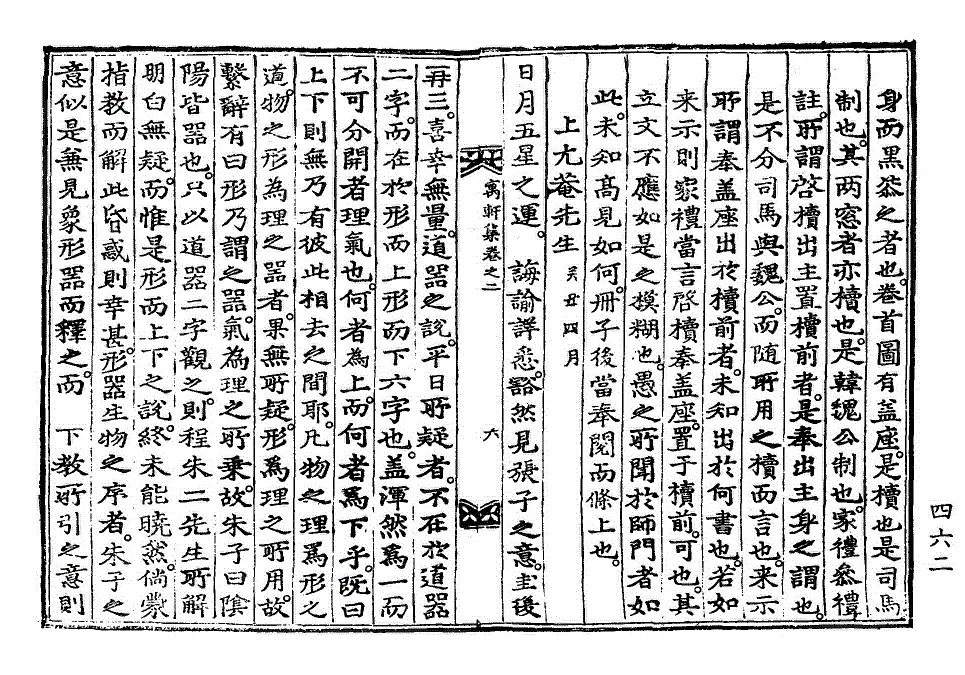 身而黑漆之者也。卷首图有盖座。是椟也是司马制也。其两窗者亦椟也。是韩魏公制也。家礼参礼注。所谓启椟出主置椟前者。是奉出主身之谓也。是不分司马与魏公。而随所用之椟而言也。来示所谓奉盖座出于椟前者。未知出于何书也。若如来示则家礼当言启椟奉盖座。置于椟前。可也。其立文不应如是之模糊也。愚之所闻于师门者如此。未知高见如何。册子后当奉阅而条上也。
身而黑漆之者也。卷首图有盖座。是椟也是司马制也。其两窗者亦椟也。是韩魏公制也。家礼参礼注。所谓启椟出主置椟前者。是奉出主身之谓也。是不分司马与魏公。而随所用之椟而言也。来示所谓奉盖座出于椟前者。未知出于何书也。若如来示则家礼当言启椟奉盖座。置于椟前。可也。其立文不应如是之模糊也。愚之所闻于师门者如此。未知高见如何。册子后当奉阅而条上也。上尤庵先生(癸丑四月)
日月五星之运。 诲谕详悉。豁然见张子之意。圭复再三。喜幸无量。道器之说。平日所疑者。不在于道器二字。而在于形而上形而下六字也。盖浑然为一而不可分开者理气也。何者为上。而何者为下乎。既曰上下则无乃有彼此相去之间耶。凡物之理为形之道。物之形为理之器者。果无所疑。形为理之所用。故系辞有曰形乃谓之器。气为理之所乘。故朱子曰阴阳皆器也。只以道器二字观之。则程朱二先生所解明白无疑。而惟是形而上下之说。终未能晓然。倘蒙指教而解此昏惑则幸甚。形器生物之序者。朱子之意似是兼见象形器而释之。而 下教所引之意则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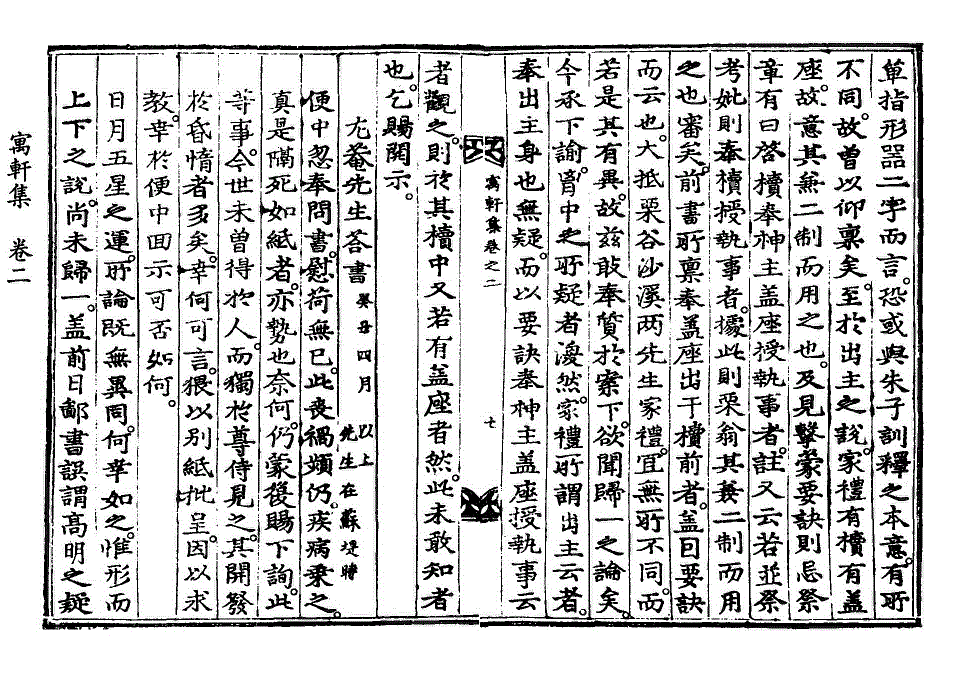 单指形器二字而言。恐或与朱子训释之本意。有所不同。故曾以仰禀矣。至于出主之说。家礼有椟有盖座。故意其兼二制而用之也。及见击蒙要诀则忌祭章有曰启椟奉神主盖座授执事者。注又云若并祭考妣则奉椟授执事者。据此则栗翁其兼二制而用之也审矣。前书所禀奉盖座出于椟前者。盖因要诀而云也。大抵栗谷沙溪两先生家礼。宜无所不同。而若是其有异。故玆敢奉质于案下。欲闻归一之论矣。今承下谕。胸中之所疑者涣然。家礼所谓出主云者。奉出主身也无疑。而以要诀奉神主盖座授执事云者观之。则于其椟中又若有盖座者然。此未敢知者也。乞赐开示。
单指形器二字而言。恐或与朱子训释之本意。有所不同。故曾以仰禀矣。至于出主之说。家礼有椟有盖座。故意其兼二制而用之也。及见击蒙要诀则忌祭章有曰启椟奉神主盖座授执事者。注又云若并祭考妣则奉椟授执事者。据此则栗翁其兼二制而用之也审矣。前书所禀奉盖座出于椟前者。盖因要诀而云也。大抵栗谷沙溪两先生家礼。宜无所不同。而若是其有异。故玆敢奉质于案下。欲闻归一之论矣。今承下谕。胸中之所疑者涣然。家礼所谓出主云者。奉出主身也无疑。而以要诀奉神主盖座授执事云者观之。则于其椟中又若有盖座者然。此未敢知者也。乞赐开示。尤庵先生答书(癸丑四月○以上先生在苏堤时)
便中忽奉问书。慰荷无已。此丧祸频仍。疾病乘之。真是隔死如纸者。亦势也奈何。仍蒙复赐下询。此等事。今世未曾得于人。而独于尊侍见之。其开发于昏惰者多矣。幸何可言。猥以别纸批呈。因以求教。幸于便中回示可否如何。
日月五星之运。所论既无异同。何幸如之。惟形而上下之说。尚未归一。盖前日鄙书误谓高明之疑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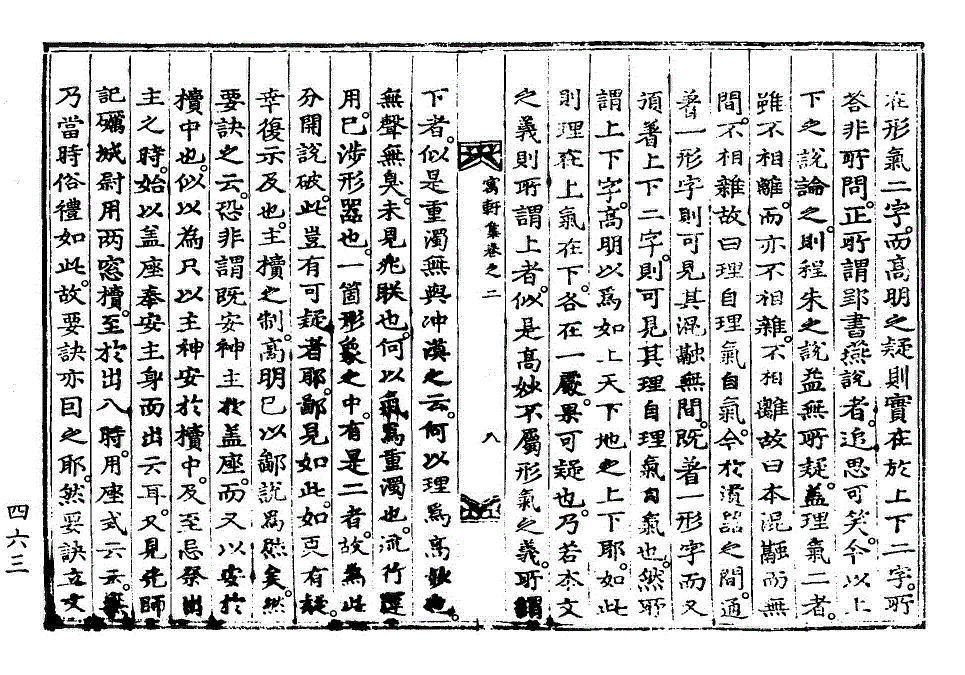 在形气二字。而高明之疑则实在于上下二字。所答非所问。正所谓郢书燕说者。追思可笑。今以上下之说论之。则程朱之说益无所疑。盖理气二者。虽不相离。而亦不相杂。不相离故曰本混融而无间。不相杂故曰理自理气自气。今于道器之间。通着一形字则可见其混融无间。既着一形字而又须着上下二字。则可见其理自理气自气也。然所谓上下字。高明以为如上天下地之上下耶。如此则理在上气在下。各在一处。果可疑也。乃若本文之义则所谓上者。似是高妙不属形气之义。所谓下者。似是重浊无与冲漠之云。何以理为高妙也。无声无臭。未见兆眹也。何以气为重浊也。流行运用。已涉形器也。一个形象之中。有是二者。故为此分开说破。此岂有可疑者耶。鄙见如此。如更有疑。幸复示及也。主椟之制。高明已以鄙说为然矣。然要诀之云。恐非谓既安神主于盖座。而又以安于椟中也。似以为只以主神安于椟中。及至忌祭出主之时。始以盖座奉安主身而出云耳。又见先师记砺城尉用两窗椟。至于出入时。用座式云云。无乃当时俗礼如此。故要诀亦因之耶。然要诀立文
在形气二字。而高明之疑则实在于上下二字。所答非所问。正所谓郢书燕说者。追思可笑。今以上下之说论之。则程朱之说益无所疑。盖理气二者。虽不相离。而亦不相杂。不相离故曰本混融而无间。不相杂故曰理自理气自气。今于道器之间。通着一形字则可见其混融无间。既着一形字而又须着上下二字。则可见其理自理气自气也。然所谓上下字。高明以为如上天下地之上下耶。如此则理在上气在下。各在一处。果可疑也。乃若本文之义则所谓上者。似是高妙不属形气之义。所谓下者。似是重浊无与冲漠之云。何以理为高妙也。无声无臭。未见兆眹也。何以气为重浊也。流行运用。已涉形器也。一个形象之中。有是二者。故为此分开说破。此岂有可疑者耶。鄙见如此。如更有疑。幸复示及也。主椟之制。高明已以鄙说为然矣。然要诀之云。恐非谓既安神主于盖座。而又以安于椟中也。似以为只以主神安于椟中。及至忌祭出主之时。始以盖座奉安主身而出云耳。又见先师记砺城尉用两窗椟。至于出入时。用座式云云。无乃当时俗礼如此。故要诀亦因之耶。然要诀立文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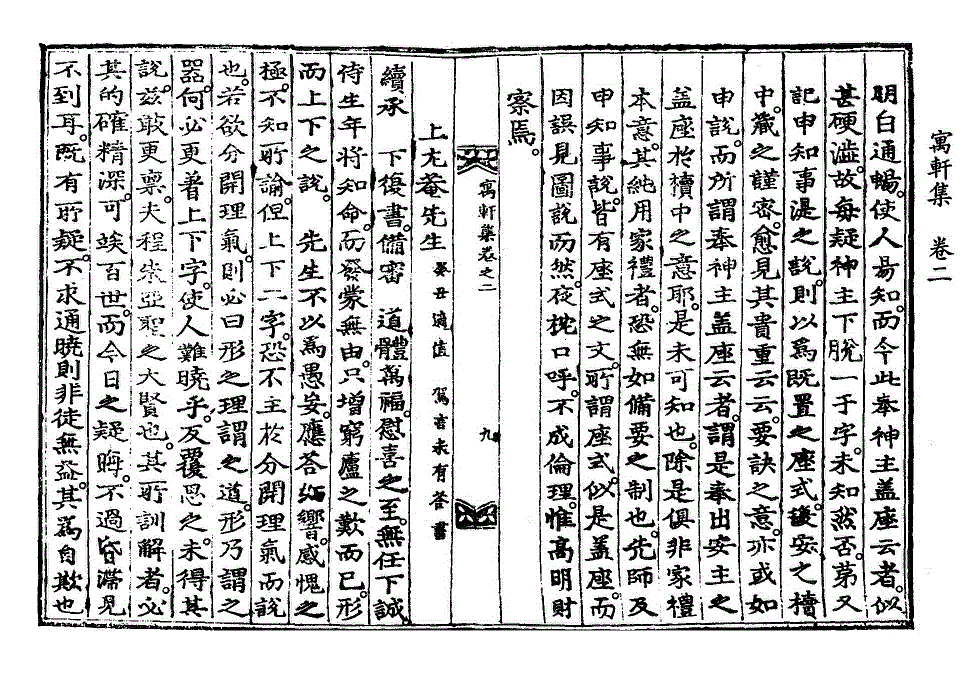 明白通畅。使人易知。而今此奉神主盖座云者。似甚硬涩。故每疑神主下脱一于字。未知然否。第又记申知事湜之说。则以为既置之座式。后安之椟中。藏之谨密。愈见其贵重云云。要诀之意。亦或如申说。而所谓奉神主盖座云者。谓是奉出安主之盖座于椟中之意耶。是未可知也。除是俱非家礼本意。其纯用家礼者。恐无如备要之制也。先师及申知事说。皆有座式之文。所谓座式。似是盖座。而因误见图说而然。夜枕口呼。不成伦理。惟高明财察焉。
明白通畅。使人易知。而今此奉神主盖座云者。似甚硬涩。故每疑神主下脱一于字。未知然否。第又记申知事湜之说。则以为既置之座式。后安之椟中。藏之谨密。愈见其贵重云云。要诀之意。亦或如申说。而所谓奉神主盖座云者。谓是奉出安主之盖座于椟中之意耶。是未可知也。除是俱非家礼本意。其纯用家礼者。恐无如备要之制也。先师及申知事说。皆有座式之文。所谓座式。似是盖座。而因误见图说而然。夜枕口呼。不成伦理。惟高明财察焉。上尤庵先生(癸丑适值○驾言未有答书)
续承 下复书。备审 道体万福。慰喜之至。无任下诚。侍生年将知命。而发蒙无由。只增穷庐之叹而已。形而上下之说。 先生不以为愚妄。应答如响。感愧之极。不知所谕。但上下二字。恐不主于分开理气而说也。若欲分开理气。则必曰形之理谓之道。形乃谓之器。何必更着上下字。使人难晓乎。反覆思之。未得其说。玆敢更禀。夫程朱亚圣之大贤也。其所训解者。必其的确精深。可俟百世。而今日之疑晦。不过昏滞见不到耳。既有所疑。不求通晓则非徒无益。其为自欺也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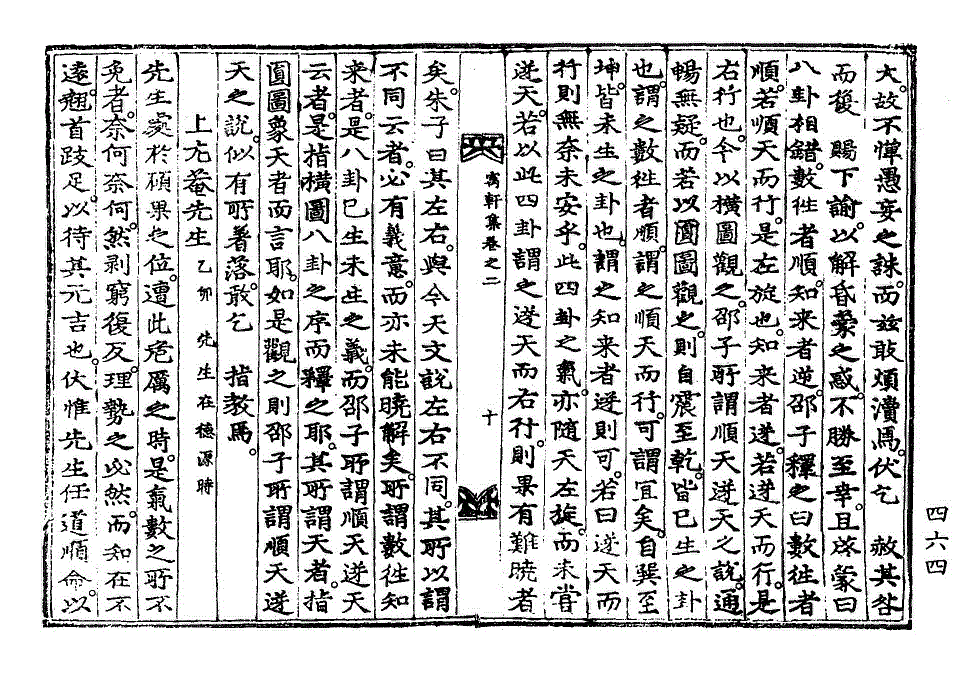 大。故不惮愚妄之诛。而玆敢烦渎焉。伏乞 赦其咎而复 赐下谕。以解昏蒙之惑。不胜至幸。且启蒙曰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释之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今以横图观之。邵子所谓顺天逆天之说。通畅无疑。而若以圆图观之。则自震至乾。皆已生之卦也。谓之数往者顺。谓之顺天而行。可谓宜矣。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也。谓之知来者逆则可。若曰逆天而行则无奈未安乎。此四卦之气。亦随天左旋。而未尝逆天。若以此四卦谓之逆天而右行。则果有难晓者矣。朱子曰其左右。与今天文说左右不同。其所以谓不同云者。必有义意。而亦未能晓解矣。所谓数往知来者。是八赴已生未生之义。而邵子所谓顺天逆天云者。是指横图八卦之序而释之耶。其所谓天者。指圆图象天者而言耶。如是观之则邵子所谓顺天逆天之说。似有所着落。敢乞 指教焉。
大。故不惮愚妄之诛。而玆敢烦渎焉。伏乞 赦其咎而复 赐下谕。以解昏蒙之惑。不胜至幸。且启蒙曰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释之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今以横图观之。邵子所谓顺天逆天之说。通畅无疑。而若以圆图观之。则自震至乾。皆已生之卦也。谓之数往者顺。谓之顺天而行。可谓宜矣。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也。谓之知来者逆则可。若曰逆天而行则无奈未安乎。此四卦之气。亦随天左旋。而未尝逆天。若以此四卦谓之逆天而右行。则果有难晓者矣。朱子曰其左右。与今天文说左右不同。其所以谓不同云者。必有义意。而亦未能晓解矣。所谓数往知来者。是八赴已生未生之义。而邵子所谓顺天逆天云者。是指横图八卦之序而释之耶。其所谓天者。指圆图象天者而言耶。如是观之则邵子所谓顺天逆天之说。似有所着落。敢乞 指教焉。上尤庵先生(乙卯○先生在德源时)
先生处于硕果之位。遭此危厉之时。是气数之所不免者。奈何奈何。然剥穷复反。理势之必然。而知在不远。翘首跂足。以待其元吉也。伏惟先生任道顺命。以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5H 页
 副区区之祝。平日咏菊一绝曰。杀尽群龙势以危。床头硕果最难支。数丛园里排霜秀。更续阳辉任自持。敢此书上。乞 赐垂览焉。
副区区之祝。平日咏菊一绝曰。杀尽群龙势以危。床头硕果最难支。数丛园里排霜秀。更续阳辉任自持。敢此书上。乞 赐垂览焉。尤庵先生答书(乙卯三月)
曾蒙不鄙。猥许诵其所闻。以资讲论之末。尔后病蛰穷谷。自去年以后。又长在吏议中。不复冒贡其愚。则所与酬酢。只论桑麻问菖蒲而已。常自耿耿于中矣。不料岭海千里之外。远赐垂札。存问死生。至如咏菊一绝。顿觉清香袭人。谁谓陶先生风韵。落此御魅之乡也。窃不胜摧谢之至也。此为臣无状。挂罹文网。今日此行已晚而犹轻矣。然如欲详言则恐添一案。置之不复道可也。前日形而上下之说。尚守前见否。程朱之训。自不如此。故曾进妄说。能不见怪否。大抵所见有所未透。则讲其所疑。固无害也。若其任已说而挥斥程朱。则其流之害。将至于稽天而不可遏。此不可不知也。僭易及此。不胜惶恐。伏惟恕谅。
上尤庵先生(乙卯五月○先生荐棘于长鬐)
自闻先生移配之后。仰屋长吁而已。当此炎极之时。虽使年富气盛之人。冒涉长途。尚且难堪。况先生衰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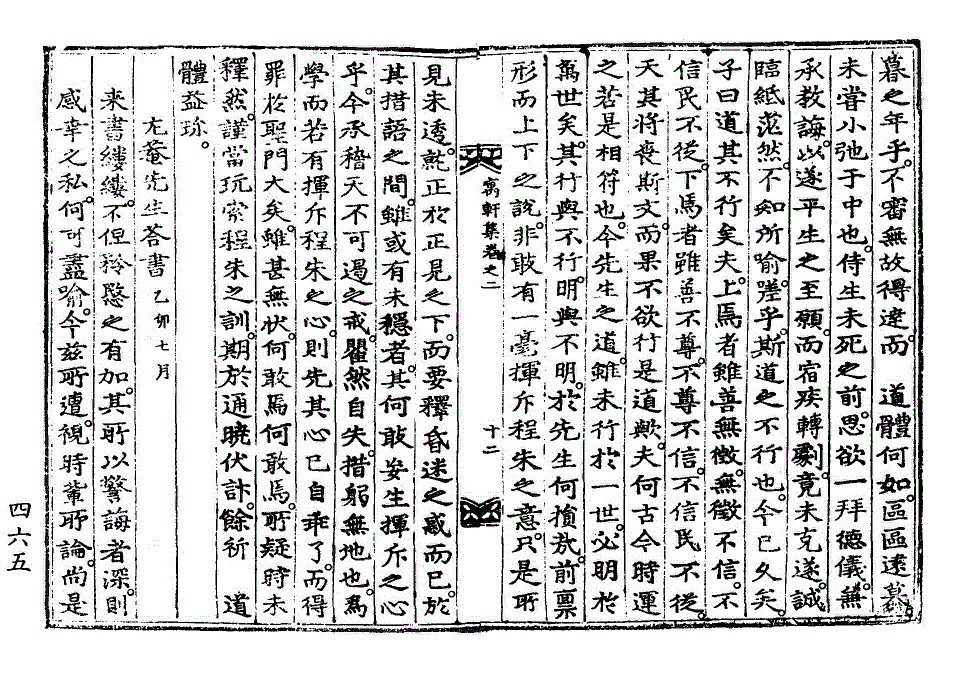 暮之年乎。不审无故得达。而 道体何如。区区远慕。未尝小弛于中也。侍生未死之前。思欲一拜德仪。兼承教诲。以遂平生之至愿。而宿疾转剧。竟未克遂。诚临纸茫然。不知所喻。嗟乎。斯道之不行也。今已久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不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不从。天其将丧斯文。而果不欲行是道欤。夫何古今时运之若是相符也。今先生之道。虽未行于一世。必明于万世矣。其行与不行。明与不明。于先生何损哉。前禀形而上下之说。非敢有一毫挥斥程朱之意。只是所见未透。就正于正见之下。而要释昏迷之惑而已。于其措语之间。虽或有未稳者。其何敢妄生挥斥之心乎。今承稽天不可遏之戒。瞿然自失。措躬无地也。为学而若有挥斥程朱之心。则先其心已自乖了。而得罪于圣门大矣。虽甚无状。何敢焉何敢焉。所疑时未释然。谨当玩索程朱之训。期于通晓伏计。馀祈 道体益珍。
暮之年乎。不审无故得达。而 道体何如。区区远慕。未尝小弛于中也。侍生未死之前。思欲一拜德仪。兼承教诲。以遂平生之至愿。而宿疾转剧。竟未克遂。诚临纸茫然。不知所喻。嗟乎。斯道之不行也。今已久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不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不从。天其将丧斯文。而果不欲行是道欤。夫何古今时运之若是相符也。今先生之道。虽未行于一世。必明于万世矣。其行与不行。明与不明。于先生何损哉。前禀形而上下之说。非敢有一毫挥斥程朱之意。只是所见未透。就正于正见之下。而要释昏迷之惑而已。于其措语之间。虽或有未稳者。其何敢妄生挥斥之心乎。今承稽天不可遏之戒。瞿然自失。措躬无地也。为学而若有挥斥程朱之心。则先其心已自乖了。而得罪于圣门大矣。虽甚无状。何敢焉何敢焉。所疑时未释然。谨当玩索程朱之训。期于通晓伏计。馀祈 道体益珍。尤庵先生答书(乙卯七月)
来书缕缕。不但矜悯之有加。其所以警诲者深。则感幸之私。何可尽喻。今玆所遭。视时辈所论。尚是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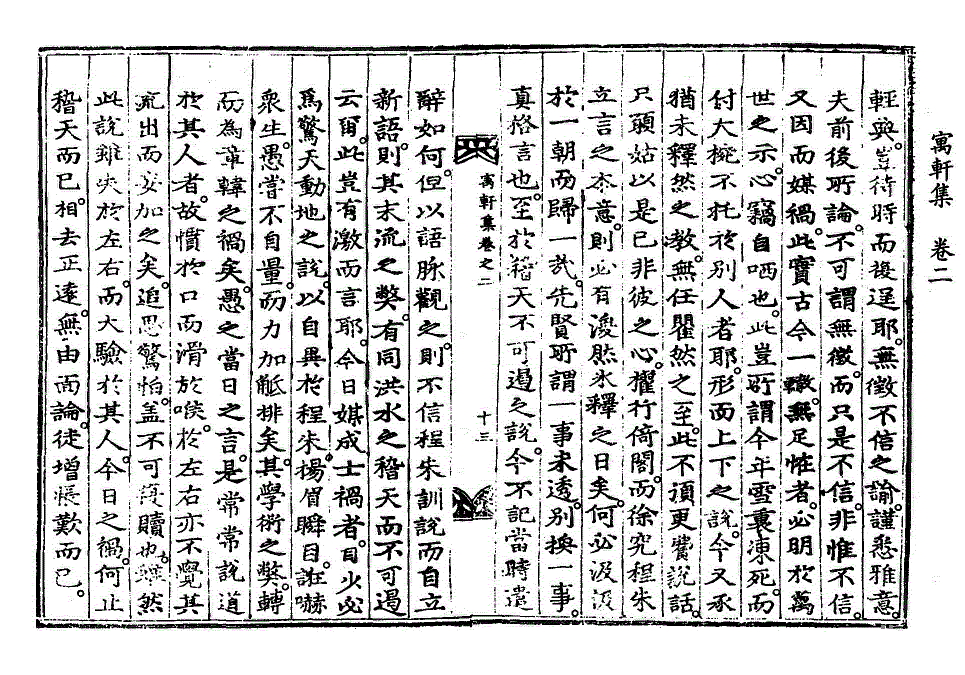 轻典。岂待时而复逞耶。无徵不信之谕。谨悉雅意。夫前后所论。不可谓无徵。而只是不信。非惟不信。又因而媒祸。此实古今一辙。无足怪者。必明于万世之示。心窃自哂也。此岂所谓今年雪里冻死。而付大碗不托于别人者耶。形而上下之说。今又承犹未释然之教。无任瞿然之至。此不须更费说话。只愿姑以是己非彼之心。权行倚阁。而徐究程朱立言之本意。则必有涣然冰释之日矣。何必汲汲于一朝而归一哉。先贤所谓一事未透。别换一事。真格言也。至于稽天不可遏之说。今不记当时遣辞如何。但以语脉观之。则不信程朱训说而自立新语。则其末流之弊。有同洪水之稽天而不可遏云尔。此岂有激而言耶。今日媒成士祸者。目少必为惊天动地之说。以自异于程朱。杨眉瞬目。诳吓众生。愚尝不自量。而力加抵排矣。其学术之弊。转而为章韩之祸矣。愚之当日之言。是常常说道于其人者。故惯于口而滑于喉。于左右亦不觉其流出而妄加之矣。追思惊怕。盖不可复赎也。虽然此说虽失于左右。而大验于其人。今日之祸。何止稽天而已。相去正远。无由面论。徒增怅叹而已。
轻典。岂待时而复逞耶。无徵不信之谕。谨悉雅意。夫前后所论。不可谓无徵。而只是不信。非惟不信。又因而媒祸。此实古今一辙。无足怪者。必明于万世之示。心窃自哂也。此岂所谓今年雪里冻死。而付大碗不托于别人者耶。形而上下之说。今又承犹未释然之教。无任瞿然之至。此不须更费说话。只愿姑以是己非彼之心。权行倚阁。而徐究程朱立言之本意。则必有涣然冰释之日矣。何必汲汲于一朝而归一哉。先贤所谓一事未透。别换一事。真格言也。至于稽天不可遏之说。今不记当时遣辞如何。但以语脉观之。则不信程朱训说而自立新语。则其末流之弊。有同洪水之稽天而不可遏云尔。此岂有激而言耶。今日媒成士祸者。目少必为惊天动地之说。以自异于程朱。杨眉瞬目。诳吓众生。愚尝不自量。而力加抵排矣。其学术之弊。转而为章韩之祸矣。愚之当日之言。是常常说道于其人者。故惯于口而滑于喉。于左右亦不觉其流出而妄加之矣。追思惊怕。盖不可复赎也。虽然此说虽失于左右。而大验于其人。今日之祸。何止稽天而已。相去正远。无由面论。徒增怅叹而已。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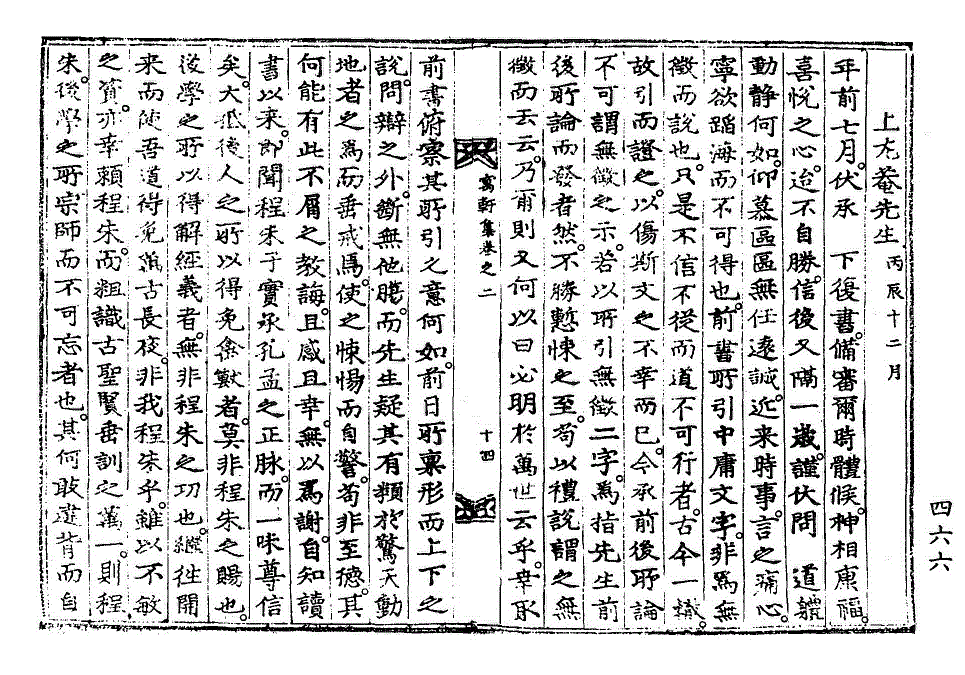 上尤庵先生(丙辰十二月)
上尤庵先生(丙辰十二月)年前七月。伏承 下复书。备审尔时体候。神相康福。喜悦之心。迨不自胜。信后又隔一岁。谨伏问 道体动静何如。仰慕区区无任远诚。近来时事。言之痛心。宁欲蹈海而不可得也。前书所引中庸文字。非为无徵而说也。只是不信不从而道不可行者。古今一辙。故引而證之。以伤斯文之不幸而已。今承前后所论不可谓无徵之示。若以所引无徵二字。为指先生前后所论而发者然。不胜惭悚之至。苟以礼说谓之无徵而云云。乃尔则又何以曰必明于万世云乎。幸取前书俯察其所引之意何如。前日所禀形而上下之说。问辩之外。断无他肠。而先生疑其有类于惊天动地者之为而垂戒焉。使之悚惕而自警。苟非至德。其何能有此不屑之教诲。且感且幸。无以骂谢。自知读书以来。即闻程朱子实承孔孟之正脉。而一味尊信矣。大抵后人之所以得免禽兽者。莫非程朱之赐也。后学之所以得解经义者。无非程朱之功也。继往开来而使吾道得免万古长夜。非我程朱乎。虽以不敏之资。亦幸赖程朱。而粗识古圣贤垂训之万一。则程朱。后学之所宗师而不可忘者也。其何敢违背而自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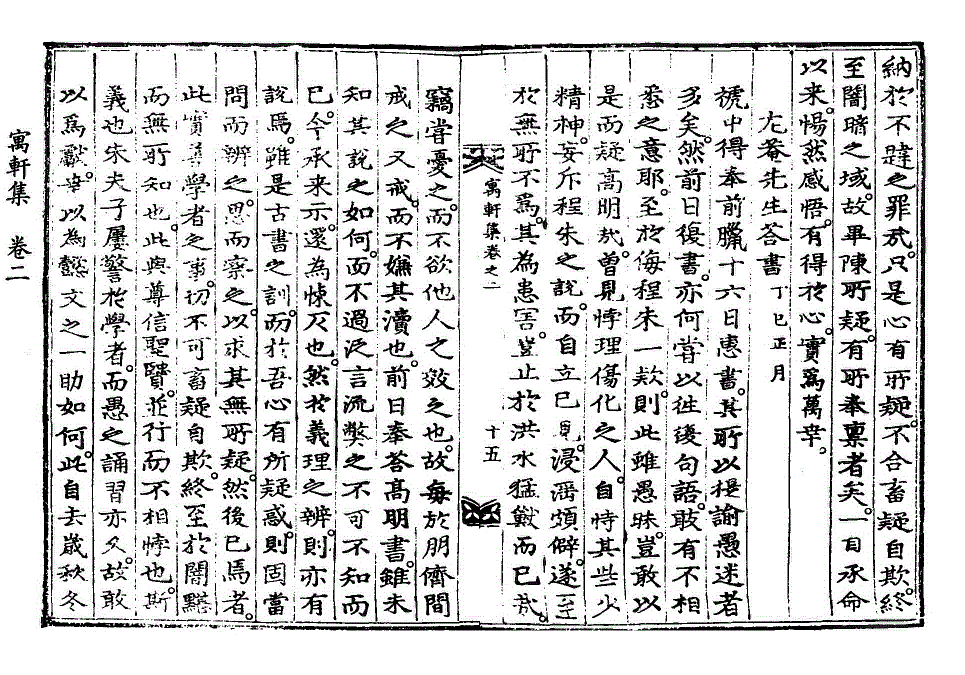 纳于不韪之罪哉。只是心有所疑。不合畜疑自欺。终至闇时之域。故毕陈所疑。有所奉禀者矣。一目承命以来。惕然感悟。有得于心。实为万幸。
纳于不韪之罪哉。只是心有所疑。不合畜疑自欺。终至闇时之域。故毕陈所疑。有所奉禀者矣。一目承命以来。惕然感悟。有得于心。实为万幸。尤庵先生答书(丁巳正月)
褫中得奉前腊十六日惠书。其所以提谕愚迷者多矣。然前日复书。亦何尝以往复句语。敢有不相悉之意耶。至于侮程朱一款。则此蜼愚昧。岂敢以是而疑高明哉。曾见悖理伤化之人。自恃其些少精神。妄斥程朱之说。而自立已见。浸淫颇僻。遂至于无所不为。其为患害。岂止于洪水猛兽而已哉。窃尝忧之。而不欲他人之效之也。故每于朋侪间戒之又戒。而不嫌其渎也。前日奉答高明书。虽未知其说之如何。而不过泛言流弊之不可不知而已。今承来示。还为悚仄也。然于义理之辨。则亦有说焉。虽是古书之训。而于吾心有所疑惑。则固当问而辨之。思而察之。以求其无所疑。然后已焉者。此实善学者之事。切不可畜疑自欺。终至于闇黮而无所知也。此与尊信圣贤。并行而不相悖也。斯义也朱夫子屡警于学者。而愚之诵习亦久。故敢以为献。幸以为懿文之一助如何。此自去岁秋冬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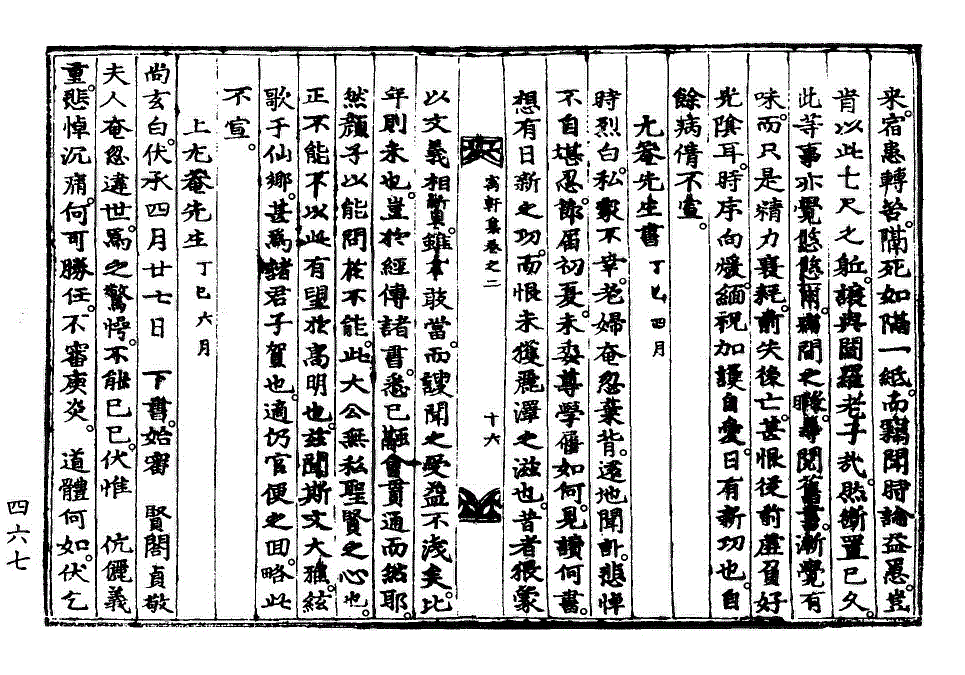 来。宿患转苦。隔死如隔一纸。而窃闻时论益急。岂肯以此七尺之躯。让与阎罗老子哉。然断置已久。此等事亦觉悠悠尔。病间之暇。寻阅旧书。渐觉有味。而只是精力衰耗。前失后亡。甚恨后前虚负好光阴耳。时序向煖。缅祝加护自爱。日有新功也。自馀病倩不宣。
来。宿患转苦。隔死如隔一纸。而窃闻时论益急。岂肯以此七尺之躯。让与阎罗老子哉。然断置已久。此等事亦觉悠悠尔。病间之暇。寻阅旧书。渐觉有味。而只是精力衰耗。前失后亡。甚恨后前虚负好光阴耳。时序向煖。缅祝加护自爱。日有新功也。自馀病倩不宣。尤庵先生书(丁巳四月)
时烈白。私家不幸。老妇奄忽弃背。远地闻讣。悲悼不自堪忍。节届初夏。未委尊学履如何。见读何书。想有日新之功。而恨未获丽泽之滋也。昔者猥蒙以文义相质。虽不敢当。而謏闻之受益不浅矣。比年则未也。岂于经传诸书。悉已融会贯通而然耶。然颜子以能问于不能。此大公无私圣贤之心也。正不能不以此有望于高明也。玆闻斯文大雅。弦歌于仙乡。甚为诸君子贺也。适仍官便之回。略此不宣。
上尤庵先生(丁巳六月)
尚玄白。伏承四月廿七日 下书。始审 贤閤贞敬夫人奄忽违世。为之惊愕。不能已已。伏惟 伉俪义重。悲悼沈痛。何可胜任。不审庚炎。 道体何如。伏乞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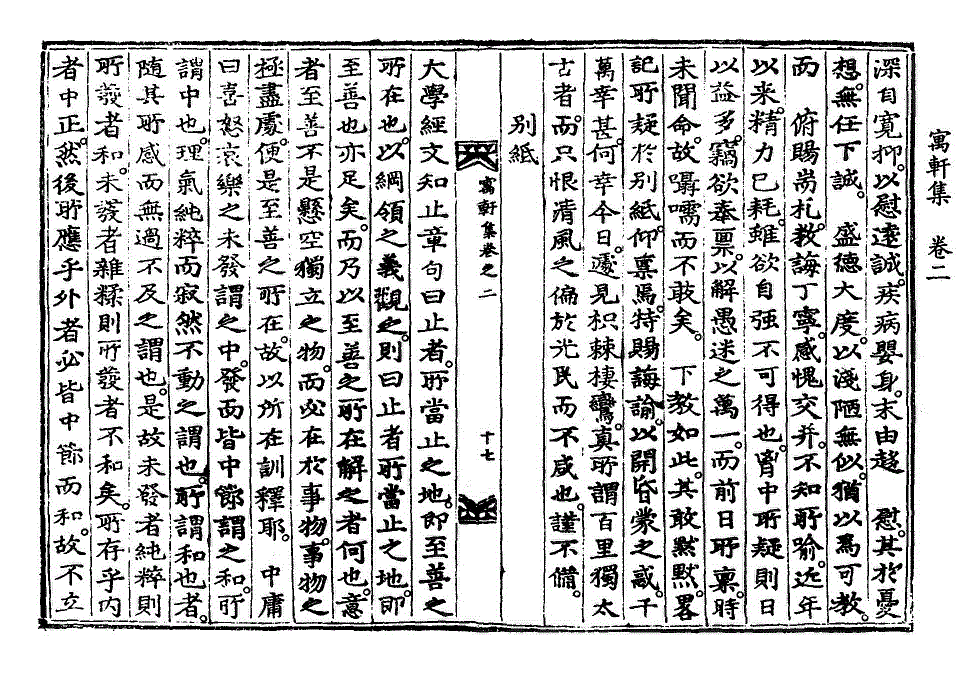 深自宽抑。以慰远诚。疾病婴身。末由趋 慰。其于忧想。无任下诚。 盛德大度。以浅陋无似。犹以为可教。而 俯赐耑札。教诲丁宁。感愧交并。不知所喻。近年以来。精力已耗。虽欲自强不可得也。胸中所疑则日以益多。窃欲奉禀。以解愚迷之万一。而前日所禀。时未闻命。故嗫嚅而不敢矣。 下教如此。其敢默默。略记所疑于别纸。仰禀焉。特赐诲谕。以开昏蒙之惑。千万幸甚。何幸今日。遽见枳棘栖鸾。真所谓百里独太古者。而只恨清风之偏于光民而不咸也。谨不备。
深自宽抑。以慰远诚。疾病婴身。末由趋 慰。其于忧想。无任下诚。 盛德大度。以浅陋无似。犹以为可教。而 俯赐耑札。教诲丁宁。感愧交并。不知所喻。近年以来。精力已耗。虽欲自强不可得也。胸中所疑则日以益多。窃欲奉禀。以解愚迷之万一。而前日所禀。时未闻命。故嗫嚅而不敢矣。 下教如此。其敢默默。略记所疑于别纸。仰禀焉。特赐诲谕。以开昏蒙之惑。千万幸甚。何幸今日。遽见枳棘栖鸾。真所谓百里独太古者。而只恨清风之偏于光民而不咸也。谨不备。别纸
大学经文知止章句曰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以纲领之义观之。则曰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也亦足矣。而乃以至善之所在解之者何也。意者至善不是悬空独立之物。而必在于事物。事物之极尽处。便是至善之所在。故以所在训释耶。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也。理气纯粹而寂然不动之谓也。所谓和也者。随其所感而无过不及之谓也。是故未发者纯粹则所发者和。未发者杂糅则所发者不和矣。所存乎内者中正。然后所应乎外者必皆中节而和。故不立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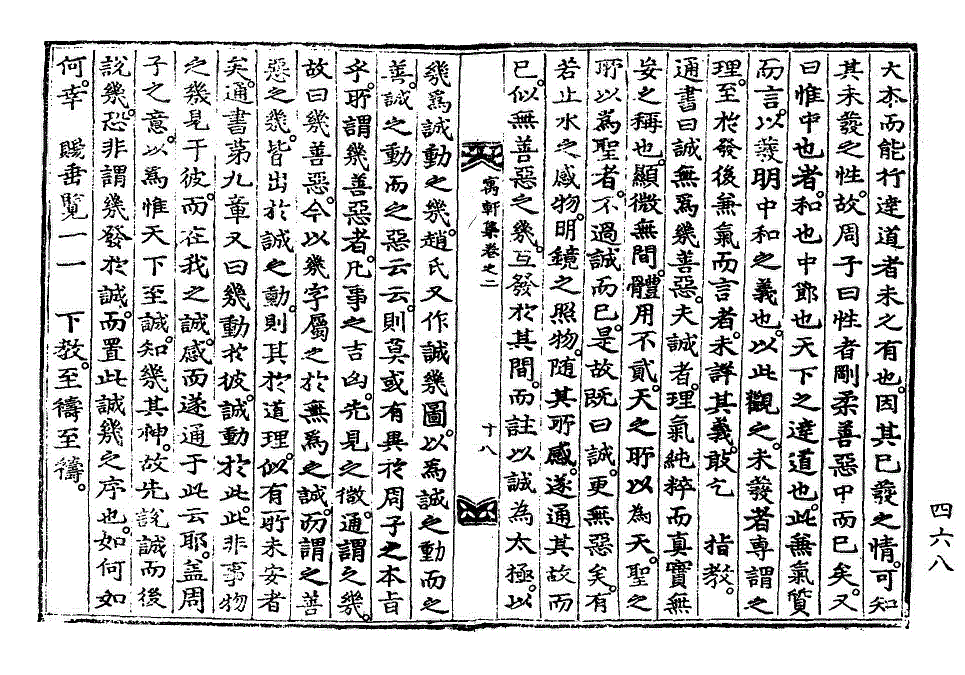 大本而能行达道者未之有也。因其已发之情。可知其未发之性。故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又曰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此兼气质而言。以发明中和之义也。以此观之。未发者专谓之理。至于发后兼气而言者。未详其义。敢乞 指教。 通书曰诚无为机善恶。夫诚者。理气纯粹而真实无妄之称也。显微无间。体用不贰。天之所以为天。圣之所以为圣者。不过诚而已。是故既曰诚。更无恶矣。有若止水之感物。明镜之照物。随其所感。遂通其故而已。似无善恶之几。互发于其间。而注以诚为太极。以几为诚动之几。赵氏又作诚几图。以为诚之动而之善。诚之动而之恶云云。则莫或有异于周子之本旨乎。所谓几善恶者。凡事之吉凶。先见之微。通谓之几。故曰几善恶。今以几字属之于无为之诚。而谓之善恶之几。皆出于诚之动。则其于道理。似有所未安者矣。通书第九章又曰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此非事物之几见于彼。而在我之诚。感而遂通于此云耶。盖周子之意。以为惟天下至诚。知几其神。故先说诚而后说几。恐非谓几发于诚。而置此诚几之序也。如何如何。幸 赐垂览一一 下教。至祷至祷。
大本而能行达道者未之有也。因其已发之情。可知其未发之性。故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又曰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此兼气质而言。以发明中和之义也。以此观之。未发者专谓之理。至于发后兼气而言者。未详其义。敢乞 指教。 通书曰诚无为机善恶。夫诚者。理气纯粹而真实无妄之称也。显微无间。体用不贰。天之所以为天。圣之所以为圣者。不过诚而已。是故既曰诚。更无恶矣。有若止水之感物。明镜之照物。随其所感。遂通其故而已。似无善恶之几。互发于其间。而注以诚为太极。以几为诚动之几。赵氏又作诚几图。以为诚之动而之善。诚之动而之恶云云。则莫或有异于周子之本旨乎。所谓几善恶者。凡事之吉凶。先见之微。通谓之几。故曰几善恶。今以几字属之于无为之诚。而谓之善恶之几。皆出于诚之动。则其于道理。似有所未安者矣。通书第九章又曰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此非事物之几见于彼。而在我之诚。感而遂通于此云耶。盖周子之意。以为惟天下至诚。知几其神。故先说诚而后说几。恐非谓几发于诚。而置此诚几之序也。如何如何。幸 赐垂览一一 下教。至祷至祷。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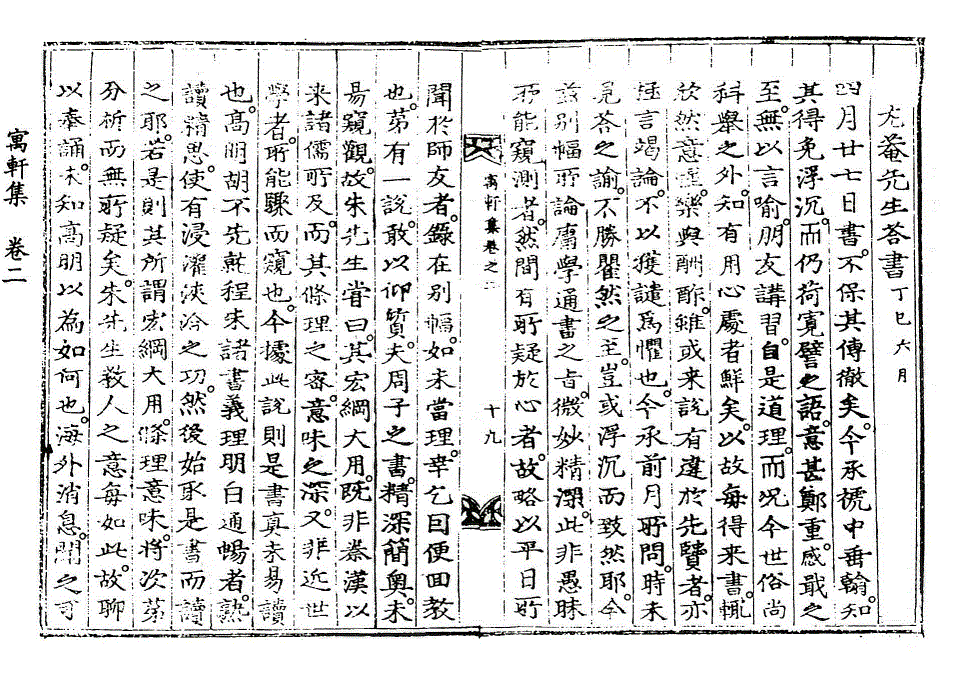 尤庵先生答书(丁巳六月)
尤庵先生答书(丁巳六月)四月廿七日书。不保其传彻矣。今承褫中垂翰。知其得免浮沈。而仍荷宽譬之语。意甚郑重。感戢之至。无以言喻。朋友讲习。自是道理。而况今世俗尚科举之外。知有用心处者鲜矣。以故每得来书。辄欣然意惺。乐与酬酢。虽或来说有违于先贤者。亦极言竭论。不以获谴为惧也。今承前月所问。时未见答之谕。不胜瞿然之至。岂或浮沈而致然耶。今玆别幅所论庸学通书之旨。微妙精深。此非愚昧所能窥测者。然间有所疑于心者。故略以平日所闻于师友者。录在别幅。如未当理。幸乞因便回教也。第有一说。敢以仰质。夫周子之书。精深简奥。未易窥观。故朱先生尝曰。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近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今据此说则是书真未易读也。高明胡不先就程朱诸书义理明白通畅者。熟读精思。使有浸灌浃洽之功。然后始取是书而读之耶。若是则其所谓宏纲大用。条理意味。将次第分析而无所疑矣。朱先生教人之意每如此。故聊以奉诵。未知高明以为如何也。海外消息。闻之可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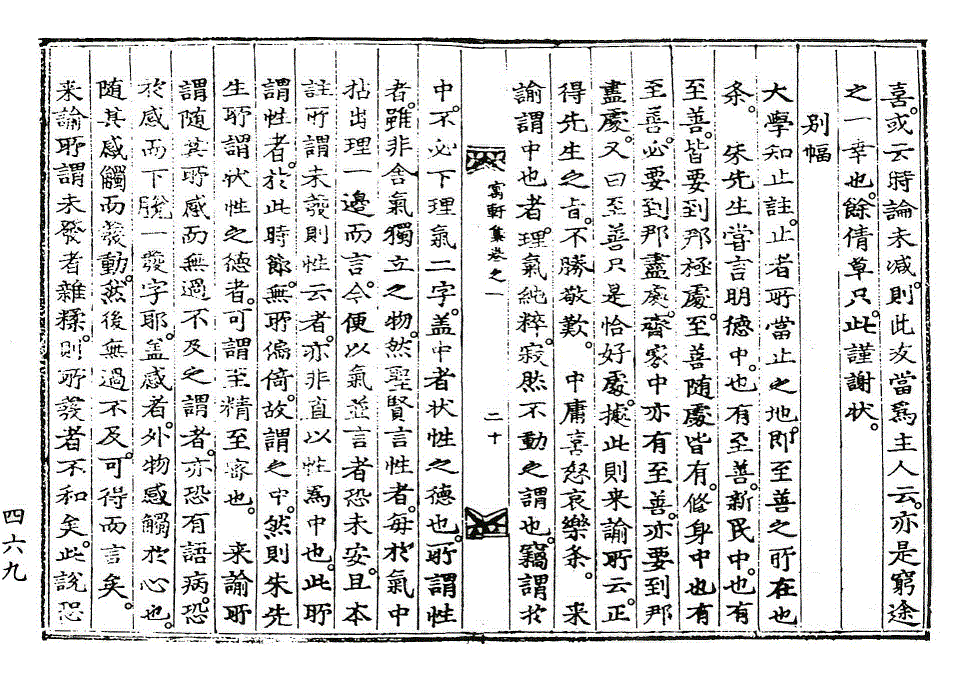 喜。或云时论未减。则此友当为主人云。亦是穷途之一幸也。馀倩草只此。谨谢状。
喜。或云时论未减。则此友当为主人云。亦是穷途之一幸也。馀倩草只此。谨谢状。别幅
大学知止注。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条。 朱先生尝言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极处。至善随处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尽处。齐家中亦有至善。亦要到那尽处。又曰至善只是恰好处。据此则来谕所云。正得先生之旨。不胜敬叹。 中庸喜怒哀乐条。 来谕谓中也者。理气纯粹。寂然不动之谓也。窃谓于中。不必下理气二字。盖中者状性之德也。所谓性者。虽非舍气独立之物。然圣贤言性者。每于气中拈出理一边而言。今便以气并言者恐未安。且本注所谓未发则性云者。亦非直以性为中也。此所谓性者。于此时节。无所偏倚。故谓之中。然则朱先生所谓状性之德者。可谓至精至密也。 来谕所谓随其所感而无过不及之谓者。亦恐有语病。恐于感而下脱一发字耶。盖感者。外物感触于心也。随其感触而发动。然后无过不及。可得而言矣。 来谕所谓未发者杂糅。则所发者不和矣。此说恐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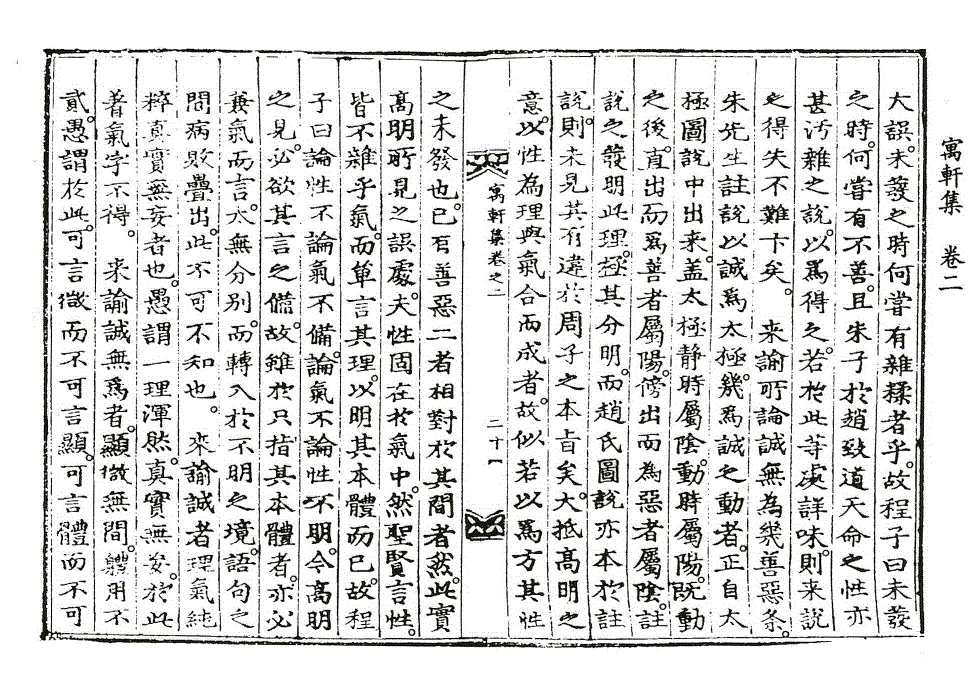 大误。未发之时何尝有杂糅者乎。故程子曰未发之时。何尝有不善。且朱子于赵致道天命之性亦甚污杂之说。以为得之。若于此等处详味。则来说之得失不难卞矣。 来谕所论诚无为几善恶条。朱先生注说以诚为太极。几为诚之动者。正自太极图说中出来。盖太极静时属阴。动时属阳。既动之后。直出而为善者属阳。傍出而为恶者属阴。注说之发明此理。极其分明。而赵氏图说亦本于注说。则未见其有违于周子之本旨矣。大抵高明之意。以性为理与气合而成者。故似若以为方其性之未发也。已有善恶二者相对于其间者然。此实高明所见之误处。夫性固在于气中。然圣贤言性。皆不杂乎气。而单言其理。以明其本体而已。故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今高明之见。必欲其言之备。故虽于只指其本体者。亦必兼气而言。太无分别。而转入于不明之境。语句之间病败叠出。此不可不知也。 来谕诚者理气纯粹真实无妄者也。愚谓一理浑然。真实无妄。于此着气字不得。 来谕诚无为者。显微无间。体用不贰。愚谓于此。可言微而不可言显。可言体而不可
大误。未发之时何尝有杂糅者乎。故程子曰未发之时。何尝有不善。且朱子于赵致道天命之性亦甚污杂之说。以为得之。若于此等处详味。则来说之得失不难卞矣。 来谕所论诚无为几善恶条。朱先生注说以诚为太极。几为诚之动者。正自太极图说中出来。盖太极静时属阴。动时属阳。既动之后。直出而为善者属阳。傍出而为恶者属阴。注说之发明此理。极其分明。而赵氏图说亦本于注说。则未见其有违于周子之本旨矣。大抵高明之意。以性为理与气合而成者。故似若以为方其性之未发也。已有善恶二者相对于其间者然。此实高明所见之误处。夫性固在于气中。然圣贤言性。皆不杂乎气。而单言其理。以明其本体而已。故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今高明之见。必欲其言之备。故虽于只指其本体者。亦必兼气而言。太无分别。而转入于不明之境。语句之间病败叠出。此不可不知也。 来谕诚者理气纯粹真实无妄者也。愚谓一理浑然。真实无妄。于此着气字不得。 来谕诚无为者。显微无间。体用不贰。愚谓于此。可言微而不可言显。可言体而不可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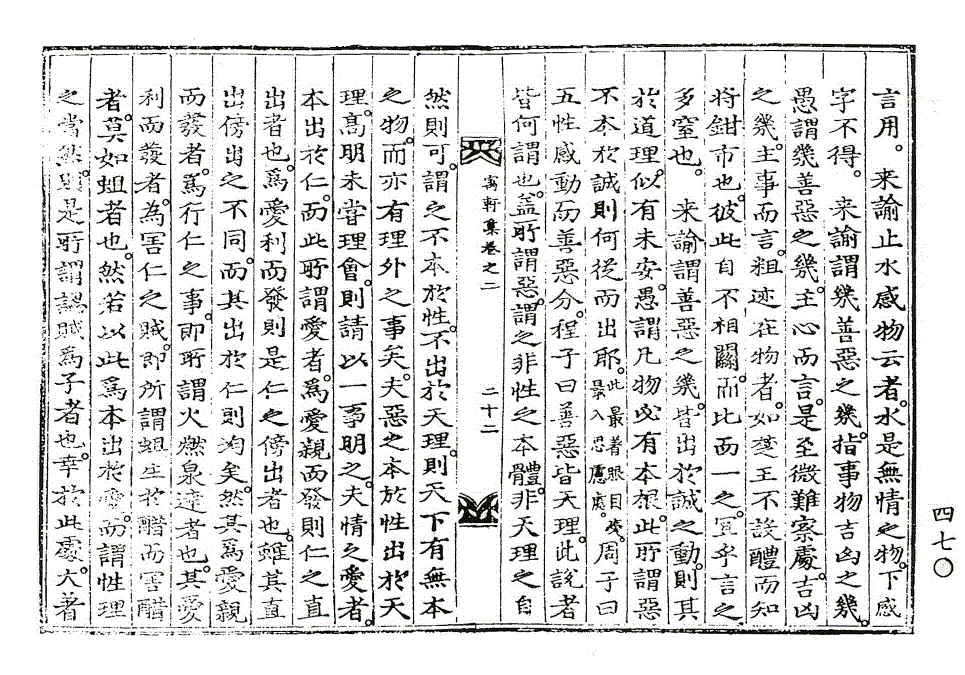 言用。 来谕止水感物云者。水是无情之物。下感字不得。 来谕谓几善恶之几。指事物吉凶之几。愚谓几善恶之几。主心而言。是至微难察处。吉凶之几。主事而言。粗迹在物者。如楚王不设醴而知将钳市也。彼此自不相关。而比而一之。宜乎言之多窒也。 来谕谓善恶之几。皆出于诚之动。则其于道理。似有未安。愚谓凡物必有本根。此所谓恶不本于诚则何从而出耶。(此最着眼目处。最入思虑处。)周子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此说者皆何谓也。盖所谓恶。谓之非性之本体。非天理之自然则可。谓之不本于性。不出于天理。则天下有无本之物。而亦有理外之事矣。夫恶之本于性出于天理。高明未尝理会。则请以一事明之。夫情之爱者。本出于仁。而此所谓爱者。为爱亲而发则仁之直出者也。为爱利而发则是仁之傍出者也。虽其直出傍出之不同。而其出于仁则均矣。然其为爱亲而发者。为行仁之事。即所谓火燃泉达者也。其爱利而发者。为害仁之贼。即所谓蛆生于醋而害醋者。莫如蛆者也。然若以此为本出于爱。而谓性理之当然。则是所谓认贼为子者也。幸于此处。大着
言用。 来谕止水感物云者。水是无情之物。下感字不得。 来谕谓几善恶之几。指事物吉凶之几。愚谓几善恶之几。主心而言。是至微难察处。吉凶之几。主事而言。粗迹在物者。如楚王不设醴而知将钳市也。彼此自不相关。而比而一之。宜乎言之多窒也。 来谕谓善恶之几。皆出于诚之动。则其于道理。似有未安。愚谓凡物必有本根。此所谓恶不本于诚则何从而出耶。(此最着眼目处。最入思虑处。)周子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程子曰善恶皆天理。此说者皆何谓也。盖所谓恶。谓之非性之本体。非天理之自然则可。谓之不本于性。不出于天理。则天下有无本之物。而亦有理外之事矣。夫恶之本于性出于天理。高明未尝理会。则请以一事明之。夫情之爱者。本出于仁。而此所谓爱者。为爱亲而发则仁之直出者也。为爱利而发则是仁之傍出者也。虽其直出傍出之不同。而其出于仁则均矣。然其为爱亲而发者。为行仁之事。即所谓火燃泉达者也。其爱利而发者。为害仁之贼。即所谓蛆生于醋而害醋者。莫如蛆者也。然若以此为本出于爱。而谓性理之当然。则是所谓认贼为子者也。幸于此处。大着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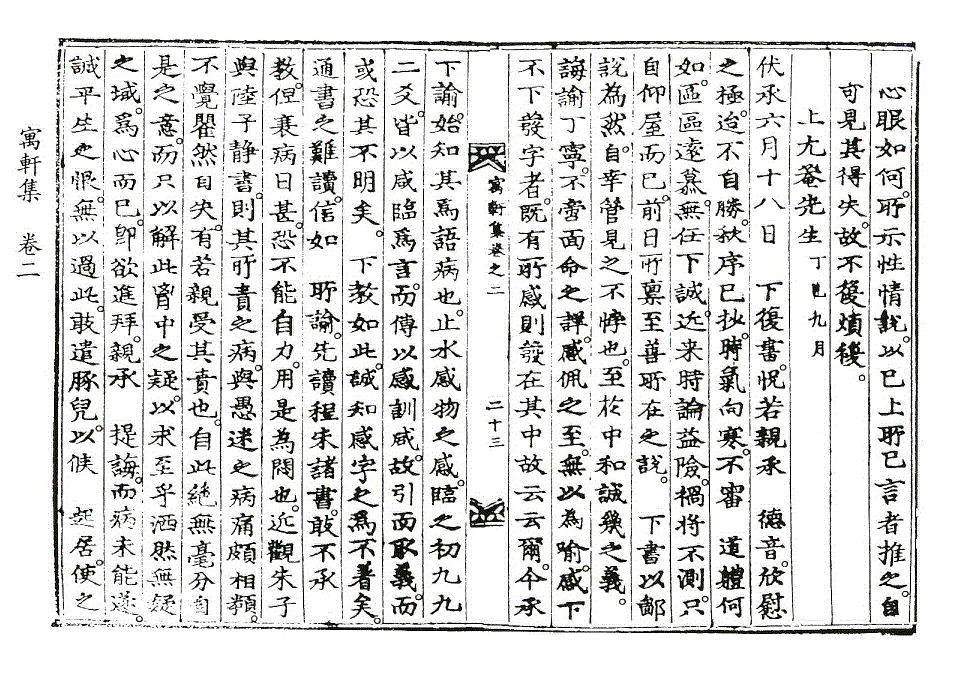 心眼如何。所示性情说。以已上所已言者推之。自可见其得失。故不复烦复。
心眼如何。所示性情说。以已上所已言者推之。自可见其得失。故不复烦复。上尤庵先生(丁巳九月)
伏承六月十八日 下复书。恍若亲承 德音。欣慰之极。迨不自胜。秋序已抄。时气向寒。不审 道体何如。区区远慕。无任下诚。近来时论益险。祸将不测。只自仰屋而已。前日所禀至善所在之说。 下书以鄙说为然。自幸管见之不悖也。至于中和诚几之义。 诲谕丁宁。不啻面命之详。感佩之至。无以为喻。感下不下发字者。既有所感则发在其中故云云尔。今承下谕。始知其为语病也。止水感物之感。临之初九九二爻。皆以咸临为言。而传以感训咸。故引而取义。而或恐其不明矣。 下教如此。诚知感字之为不着矣。通书之难读。信如 所谕。先读程朱诸书。敢不承 教。但衰病日甚。恐不能自力。用是为闷也。近观朱子与陆子静书。则其所责之病。与愚迷之病痛颇相类。不觉瞿然自失。有若亲受其责也。自此绝无毫分自是之意。而只以解此胸中之疑。以求至乎洒然无疑之域。为心而已。即欲进拜。亲承 提诲。而病未能遂。诚平生之恨。无以过此。敢遣豚儿。以候 起居。使之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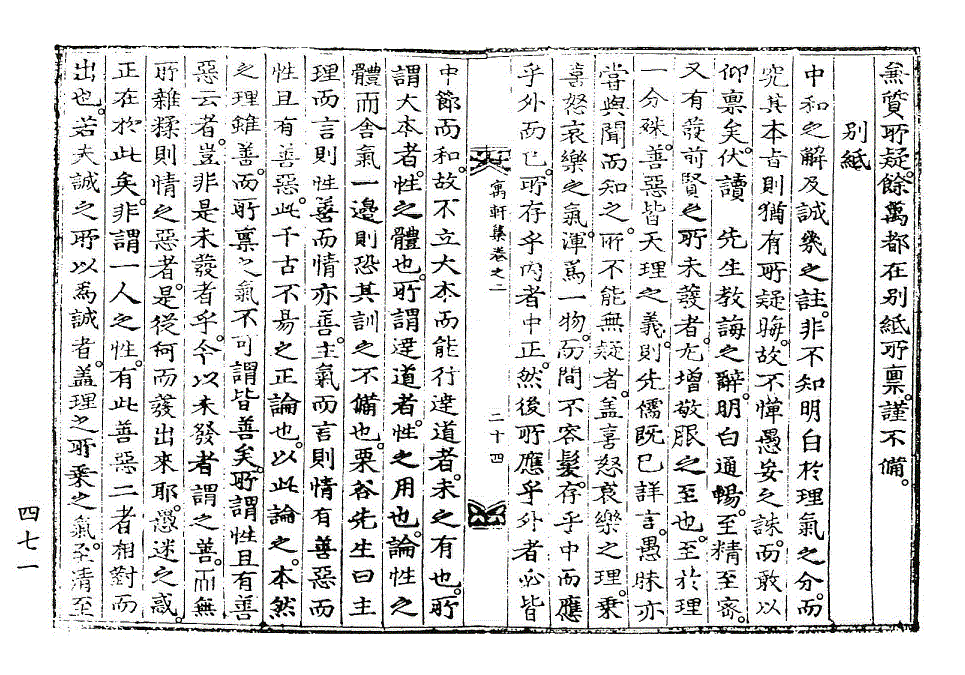 兼质所疑。馀万都在别纸所禀。谨不备。
兼质所疑。馀万都在别纸所禀。谨不备。别纸
中和之解及诚几之注。非不知明白于理气之分。而究其本旨则犹有所疑晦。故不惮愚妄之诛。而敢以仰禀矣。伏读 先生教诲之辞。明白通畅。至精至密。又有发前贤之所未发者。尤增敬服之至也。至于理一分殊。善恶皆天理之义。则先儒既已详言。愚昧亦尝与闻而知之。所不能无疑者。盖喜怒哀乐之理。乘喜怒哀乐之气。浑为一物。而间不容发。存乎中而应乎外而已。所存乎内者中正。然后所应乎外者必皆中节而和。故不立大本而能行达道者。未之有也。所谓大本者。性之体也。所谓达道者。性之用也。论性之体而舍气一边则恐其训之不备也。栗谷先生曰主理而言则性善而情亦善。主气而言则情有善恶而性且有善恶。此千古不易之正论也。以此论之。本然之理虽善。而所禀之气不可谓皆善矣。所谓性且有善恶云者。岂非是未发者乎。今以未发者谓之善。而无所杂糅则情之恶者。是从何而发出来耶。愚迷之惑。正在于此矣。非谓一人之性。有此善恶二者相对而出也。若夫诚之所以为诚者。盖理之所乘之气。至清至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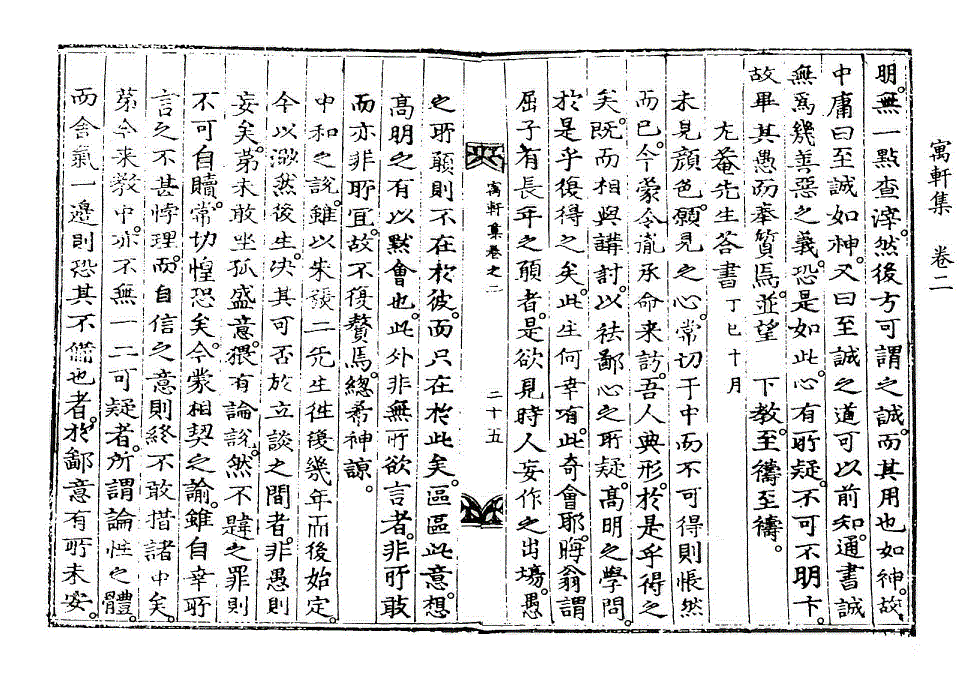 明。无一点查滓。然后方可谓之诚。而其用也如神。故中庸曰至诚如神。又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通书诚无为几善恶之义。恐是如此。心有所疑。不可不明卞。故毕其愚而奉质焉。并望 下教。至祷至祷。
明。无一点查滓。然后方可谓之诚。而其用也如神。故中庸曰至诚如神。又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通书诚无为几善恶之义。恐是如此。心有所疑。不可不明卞。故毕其愚而奉质焉。并望 下教。至祷至祷。尤庵先生答书(丁巳十月)
未见颜色。愿见之心。常切于中而不可得则怅然而已。今蒙令胤承命来访。吾人典形。于是乎得之矣。既而相与讲讨。以祛鄙心之所疑。高明之学问。于是乎复得之矣。此生何幸有。此奇会耶。晦翁谓屈子有长年之愿者。是欲见时人妄作之出场。愚之所愿则不在于彼。而只在于此矣。区区此意。想高明之有以默会也。此外非无所欲言者。非所敢而亦非所宜。故不复赘焉。总希神谅。
中和之说。虽以朱张二先生往复几年而后始定。今以渺然后生。决其可否于立谈之间者。非愚则妄矣。第未敢坐孤盛意。猥有论说。然不韪之罪则不可自赎。常切惶恐矣。今蒙相契之谕。虽自幸所言之不甚悖理。而自信之意则终不敢措诸中矣。第今来教中。亦不无一二可疑者。所谓论性之体。而舍气一边则恐其不备也者。于鄙意有所未安。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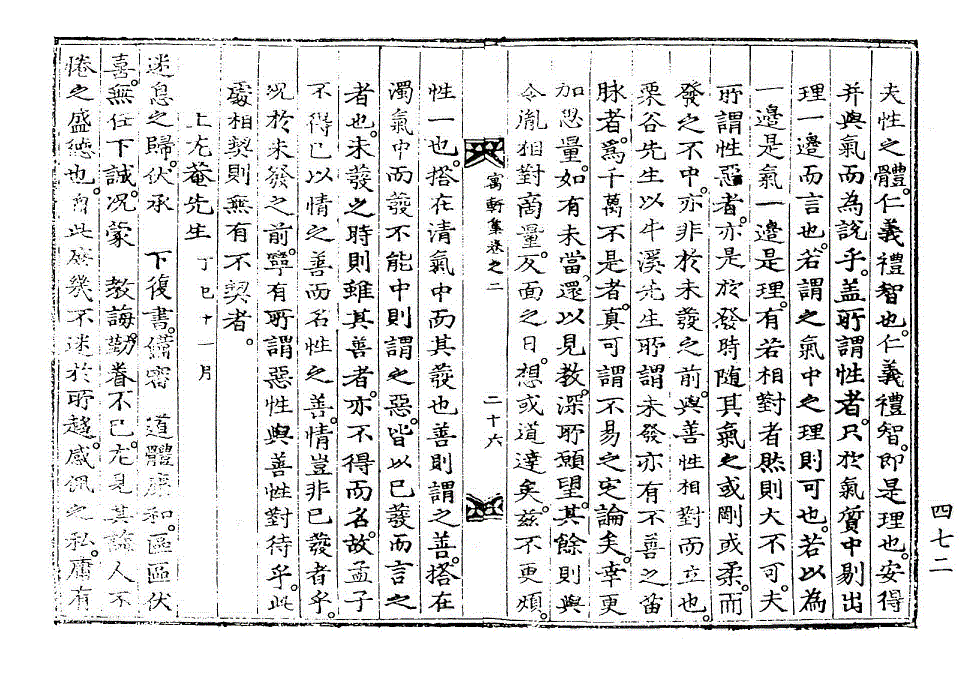 夫性之体。仁义礼智也。仁义礼智。即是理也。安得并与气而为说乎。盖所谓性者。只于气质中剔出理一边而言也。若谓之气中之理则可也。若以为一边是气一边是理。有若相对者然则大不可。夫所谓性恶者。亦是于发时随其气之或刚或柔。而发之不中。亦非于未发之前。与善性相对而立也。栗谷先生以牛溪先生所谓未发亦有不善之苗脉者。为千万不是者。真可谓不易之定论矣。幸更加思量。如有未当。还以见教。深所愿望。其馀则与令胤相对啇量。反面之日。想或道达矣。玆不更烦。性一也。搭在清气中而其发也善则谓之善。搭在浊气中而发不能中则谓之恶。皆以已发而言之者也。未发之时则虽其善者。亦不得而名。故孟子不得已以情之善而名性之善。情岂非已发者乎。况于未发之前。宁有所谓恶性与善性对待乎。此处相契则无有不契者。
夫性之体。仁义礼智也。仁义礼智。即是理也。安得并与气而为说乎。盖所谓性者。只于气质中剔出理一边而言也。若谓之气中之理则可也。若以为一边是气一边是理。有若相对者然则大不可。夫所谓性恶者。亦是于发时随其气之或刚或柔。而发之不中。亦非于未发之前。与善性相对而立也。栗谷先生以牛溪先生所谓未发亦有不善之苗脉者。为千万不是者。真可谓不易之定论矣。幸更加思量。如有未当。还以见教。深所愿望。其馀则与令胤相对啇量。反面之日。想或道达矣。玆不更烦。性一也。搭在清气中而其发也善则谓之善。搭在浊气中而发不能中则谓之恶。皆以已发而言之者也。未发之时则虽其善者。亦不得而名。故孟子不得已以情之善而名性之善。情岂非已发者乎。况于未发之前。宁有所谓恶性与善性对待乎。此处相契则无有不契者。上尤庵先生(丁巳十一月)
迷息之归。伏承 下复书。备审 道体康和。区区伏喜。无任下诚。况蒙 教诲。勤眷不已。尤见其诲人不惓之盛德也。自此庶几不迷于所趋。感佩之私。庸有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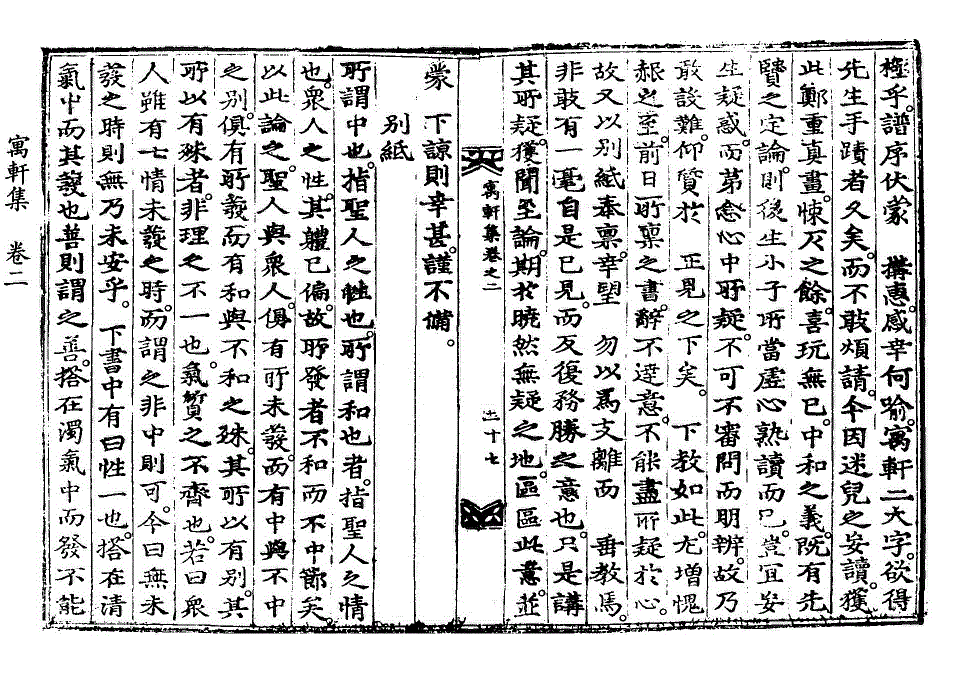 极乎。谱序伏蒙 搆惠。感幸何喻。寓轩二大字。欲得先生手迹者久矣。而不敢烦请。今因迷儿之妄读。获此郑重真画。悚仄之馀。喜玩无已。中和之义。既有先贤之定论。则后生小子所当虚心熟读而已。岂宜妄生疑惑。而第念心中所疑。不可不审问而明辨。故乃敢设难。仰质于 正见之下矣。 下教如此。尤增愧赧之至。前日所禀之书。辞不达意。不能尽所疑于心。故又以别纸奉禀。幸望 勿以为支离而 垂教焉。非敢有一毫自是己见。而反复务胜之意也。只是讲其所疑。获闻至论。期于晓然无疑之地。区区此意。并蒙 下谅则幸甚。谨不备。
极乎。谱序伏蒙 搆惠。感幸何喻。寓轩二大字。欲得先生手迹者久矣。而不敢烦请。今因迷儿之妄读。获此郑重真画。悚仄之馀。喜玩无已。中和之义。既有先贤之定论。则后生小子所当虚心熟读而已。岂宜妄生疑惑。而第念心中所疑。不可不审问而明辨。故乃敢设难。仰质于 正见之下矣。 下教如此。尤增愧赧之至。前日所禀之书。辞不达意。不能尽所疑于心。故又以别纸奉禀。幸望 勿以为支离而 垂教焉。非敢有一毫自是己见。而反复务胜之意也。只是讲其所疑。获闻至论。期于晓然无疑之地。区区此意。并蒙 下谅则幸甚。谨不备。别纸
所谓中也。指圣人之性也。所谓和也者。指圣人之情也。众人之性。其体已偏。故所发者不和而不中节矣。以此论之。圣人与众人。俱有所未发。而有中与不中之别。俱有所发而有和与不和之殊。其所以有别。其所以有殊者。非理之不一也。气质之不齐也。若曰众人虽有七情未发之时。而谓之非中则可。今曰无未发之时则无乃未安乎。下书中有曰性一也。搭在清气中而其发也善则谓之善。搭在浊气中而发不能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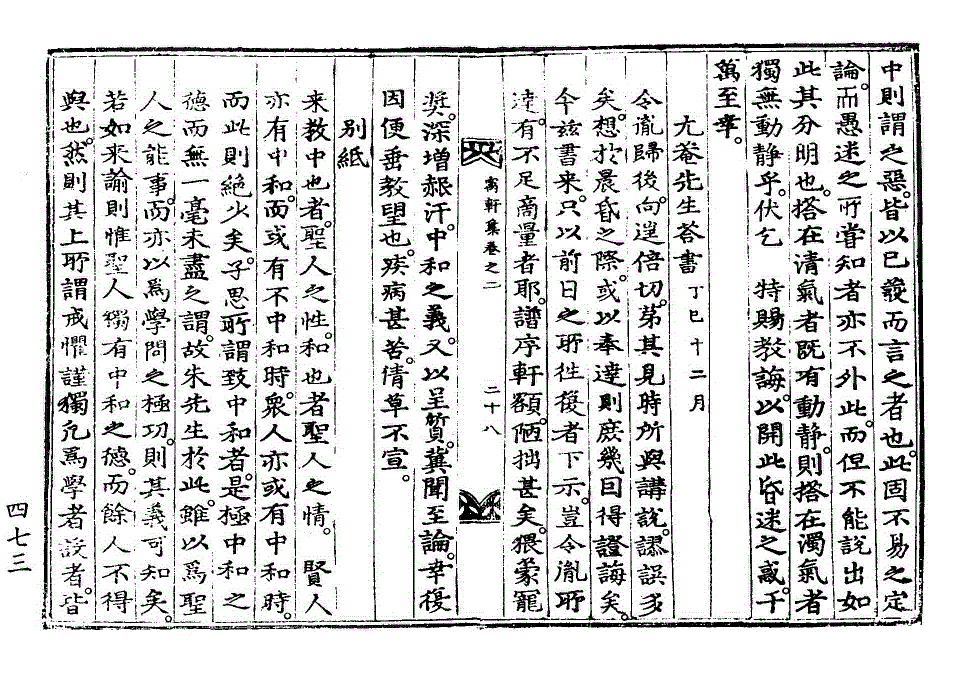 中则谓之恶。皆以已发而言之者也。此固不易之定论。而愚迷之所尝知者亦不外此。而但不能说出如此其分明也。搭在清气者既有动静。则搭在浊气者独无动静乎。伏乞 特赐教诲。以开此昏迷之惑。千万至幸。
中则谓之恶。皆以已发而言之者也。此固不易之定论。而愚迷之所尝知者亦不外此。而但不能说出如此其分明也。搭在清气者既有动静。则搭在浊气者独无动静乎。伏乞 特赐教诲。以开此昏迷之惑。千万至幸。尤庵先生答书(丁巳十二月)
令胤归后。向𨓏倍切。第其见时所与讲说。谬误多矣。想于晨昏之际。或以奉达则庶几因得證诲矣。今玆书来。只以前日之所往复者下示。岂令胤所达。有不足啇量者耶。谱序轩额。陋拙甚矣。猥蒙宠奖。深增赧汗。中和之义。又以呈质。冀闻至论。幸复因便垂教望也。疾病甚苦。倩草不宣。
别纸
来教中也者。圣人之性。和也者圣人之情。 贤人亦有中和。而或有不中和时。众人亦或有中和时。而此则绝少矣。子思所谓致中和者。是极中和之德而无一毫未尽之谓。故朱先生于此。虽以为圣人之能事。而亦以为学问之极功。则其义可知矣。若如来谕则惟圣人独有中和之德。而馀人不得与也。然则其上所谓戒惧谨独凡为学者设者。皆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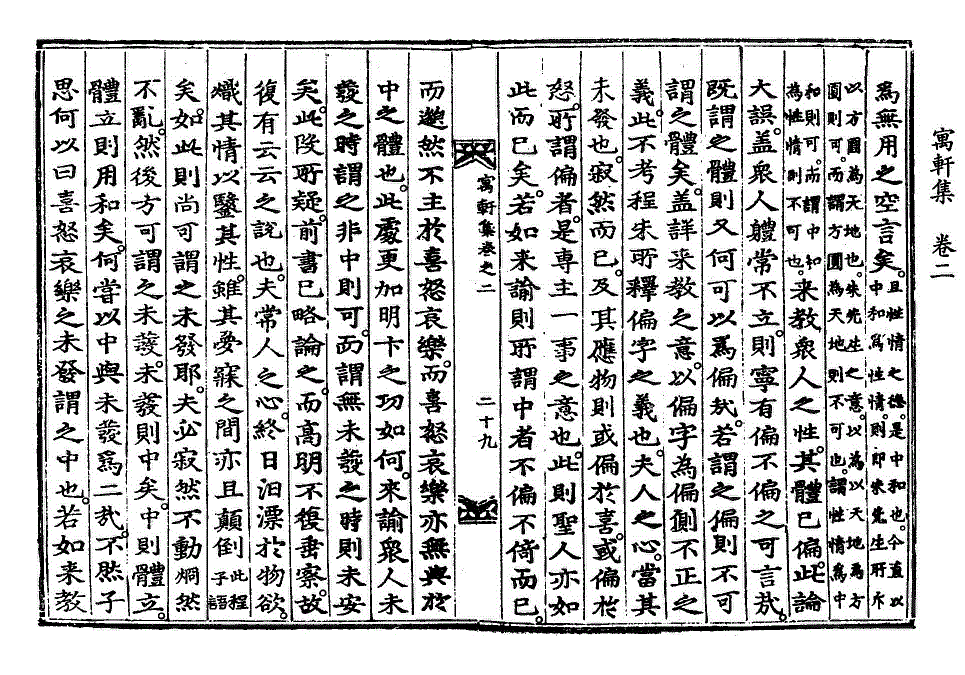 为无用之空言矣。(且性情之德。是中和也。今直以中和为性情。则即朱先生所斥以方圆为天地也。朱先生之意。以为以天地为方圆则可。而谓方圆为天地则不可也。谓性情为中和则可。而谓中和为性情则不可也。)来教众人之性。其体已偏。此论大误。盖众人体常不立。则宁有偏不偏之可言哉。既谓之体则又何可以为偏哉。若谓之偏则不可谓之体矣。盖详来教之意。以偏字为偏侧不正之义。此不考程朱所释偏字之义也。夫人之心。当其未发也。寂然而已。及其应物则或偏于喜。或偏于怒。所谓偏者。是专主一事之意也。此则圣人亦如此而已矣。若如来谕则所谓中者不偏不倚而已。而邈然不主于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亦无与于中之体也。此处更加明卞之功如何。来谕众人未发之时谓之非中则可。而谓无未发之时则未安矣。此段所疑。前书已略论之。而高明不复垂察。故复有云云之说也。夫常人之心。终日汨漂于物欲。炽其情以凿其性。虽其梦寐之间亦且颠倒(此程子语)矣。如此则尚可谓之未发耶。夫必寂然不动炯然不乱。然后方可谓之未发。未发则中矣。中则体立。体立则用和矣。何尝以中与未发为二哉。不然子思何以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若如来教
为无用之空言矣。(且性情之德。是中和也。今直以中和为性情。则即朱先生所斥以方圆为天地也。朱先生之意。以为以天地为方圆则可。而谓方圆为天地则不可也。谓性情为中和则可。而谓中和为性情则不可也。)来教众人之性。其体已偏。此论大误。盖众人体常不立。则宁有偏不偏之可言哉。既谓之体则又何可以为偏哉。若谓之偏则不可谓之体矣。盖详来教之意。以偏字为偏侧不正之义。此不考程朱所释偏字之义也。夫人之心。当其未发也。寂然而已。及其应物则或偏于喜。或偏于怒。所谓偏者。是专主一事之意也。此则圣人亦如此而已矣。若如来谕则所谓中者不偏不倚而已。而邈然不主于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亦无与于中之体也。此处更加明卞之功如何。来谕众人未发之时谓之非中则可。而谓无未发之时则未安矣。此段所疑。前书已略论之。而高明不复垂察。故复有云云之说也。夫常人之心。终日汨漂于物欲。炽其情以凿其性。虽其梦寐之间亦且颠倒(此程子语)矣。如此则尚可谓之未发耶。夫必寂然不动炯然不乱。然后方可谓之未发。未发则中矣。中则体立。体立则用和矣。何尝以中与未发为二哉。不然子思何以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若如来教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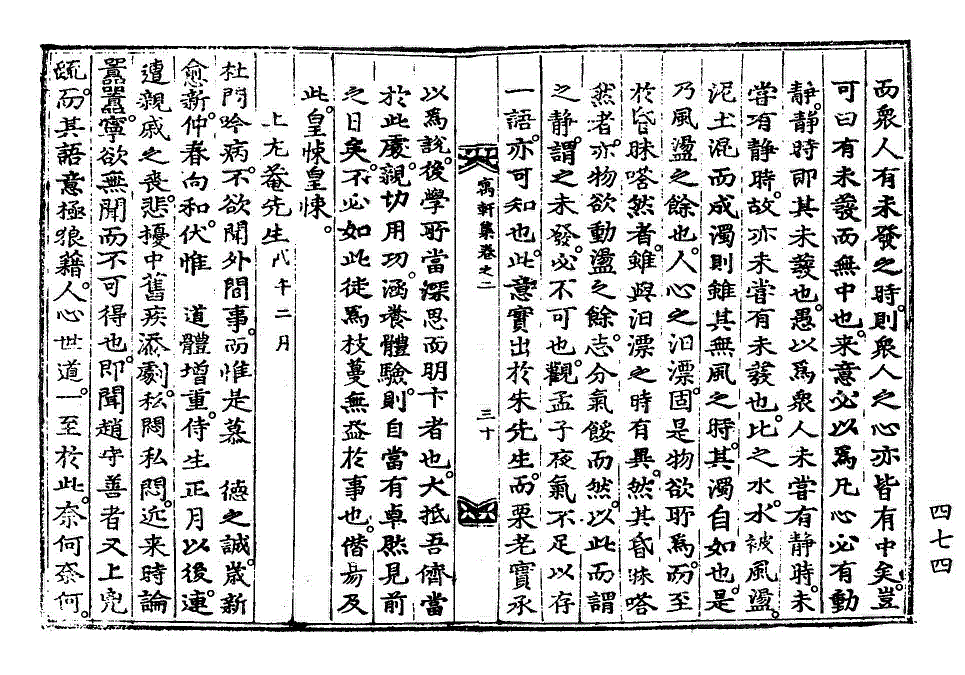 而众人有未发之时。则众人之心亦皆有中矣。岂可曰有未发而无中也。来意必以为凡心必有动静。静时即其未发也。愚以为众人未尝有静时。未尝有静时。故亦未尝有未发也。比之水。水被风荡。泥土混而成浊则虽其无风之时。其浊自如也。是乃风荡之馀也。人心之汨漂。固是物欲所为。而至于昏昧嗒然者。虽与汨漂之时有异。然其昏昧嗒然者。亦物欲动荡之馀。志分气馁而然。以此而谓之静。谓之未发。必不可也。观孟子夜气不足以存一语。亦可知也。此意实出于朱先生。而栗老实承以为说。后学所当深思而明卞者也。大抵吾侪当于此处。亲切用功。涵养体验。则自当有卓然见前之日矣。不必如此徒为枝蔓无益于事也。僭易及此。皇悚皇悚。
而众人有未发之时。则众人之心亦皆有中矣。岂可曰有未发而无中也。来意必以为凡心必有动静。静时即其未发也。愚以为众人未尝有静时。未尝有静时。故亦未尝有未发也。比之水。水被风荡。泥土混而成浊则虽其无风之时。其浊自如也。是乃风荡之馀也。人心之汨漂。固是物欲所为。而至于昏昧嗒然者。虽与汨漂之时有异。然其昏昧嗒然者。亦物欲动荡之馀。志分气馁而然。以此而谓之静。谓之未发。必不可也。观孟子夜气不足以存一语。亦可知也。此意实出于朱先生。而栗老实承以为说。后学所当深思而明卞者也。大抵吾侪当于此处。亲切用功。涵养体验。则自当有卓然见前之日矣。不必如此徒为枝蔓无益于事也。僭易及此。皇悚皇悚。上尤庵先生(戊午二月)
杜门吟病。不欲闻外间事。而惟是慕 德之诚。岁新愈新。仲春向和。伏惟 道体增重。侍生正月以后。连遭亲戚之丧。悲扰中旧疾添剧。私闷私闷。近来时论嚣嚣。宁欲无闻而不可得也。即闻赵守善者又上凶疏。而其语意极狼藉。人心世道。一至于此。奈何奈何。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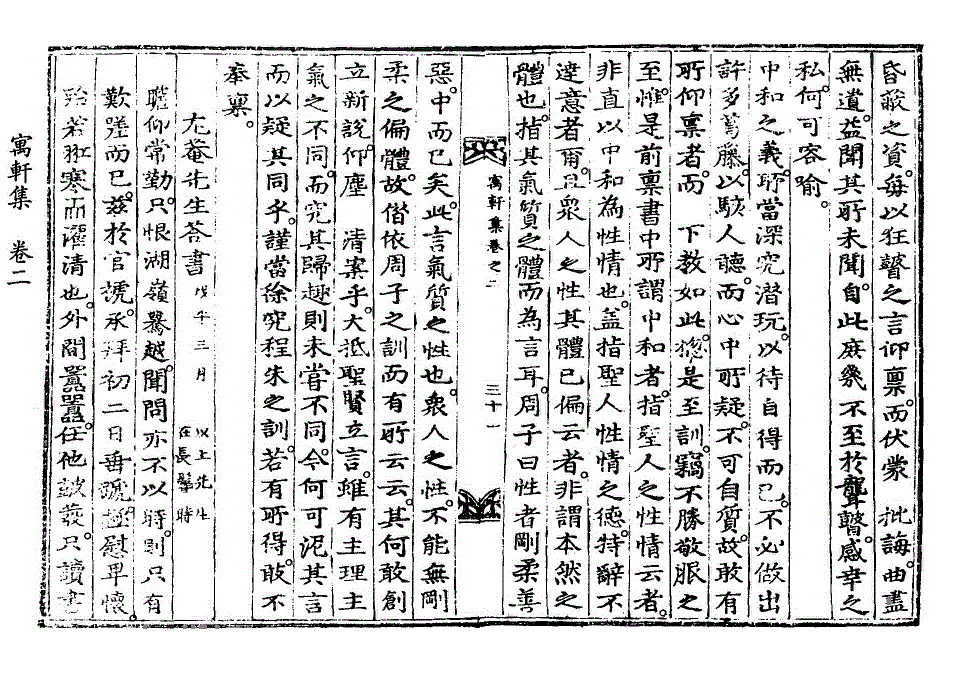 昏蔽之资。每以狂瞽之言仰禀。而伏蒙 批诲。曲尽无遗。益闻其所未闻。自此庶几不至于聋瞽。感幸之私。何可容喻。
昏蔽之资。每以狂瞽之言仰禀。而伏蒙 批诲。曲尽无遗。益闻其所未闻。自此庶几不至于聋瞽。感幸之私。何可容喻。中和之义。所当深究潜玩。以待自得而已。不必做出许多葛藤。以骇人听。而心中所疑。不可自质。故敢有所仰禀者。而 下教如此。总是至训。窃不胜敬服之至。惟是前禀书中所谓中和者。指圣人之性情云者。非直以中和为性情也。盖指圣人性情之德。特辞不达意者尔。且众人之性其体已偏云者。非谓本然之体也。指其气质之体而为言耳。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此言气质之性也。众人之性。不能无刚柔之偏体。故僭依周子之训而有所云云。其何敢创立新说。仰尘 清案乎。大抵圣贤立言。虽有主理主气之不同。而究其归趣则未尝不同。今何可泥其言而以疑其同乎。谨当徐究程朱之训。若有所得。敢不奉禀。
尤庵先生答书(戊午三月○以上先生在长鬐时)
瞻仰常勤。只恨湖岭蓦越。闻问亦不以时。则只有叹嗟而已。玆于官褫。承拜初二日垂蹄。极慰卑怀。殆若羾寒而灌清也。外间嚣嚣。任他鼓发。只读书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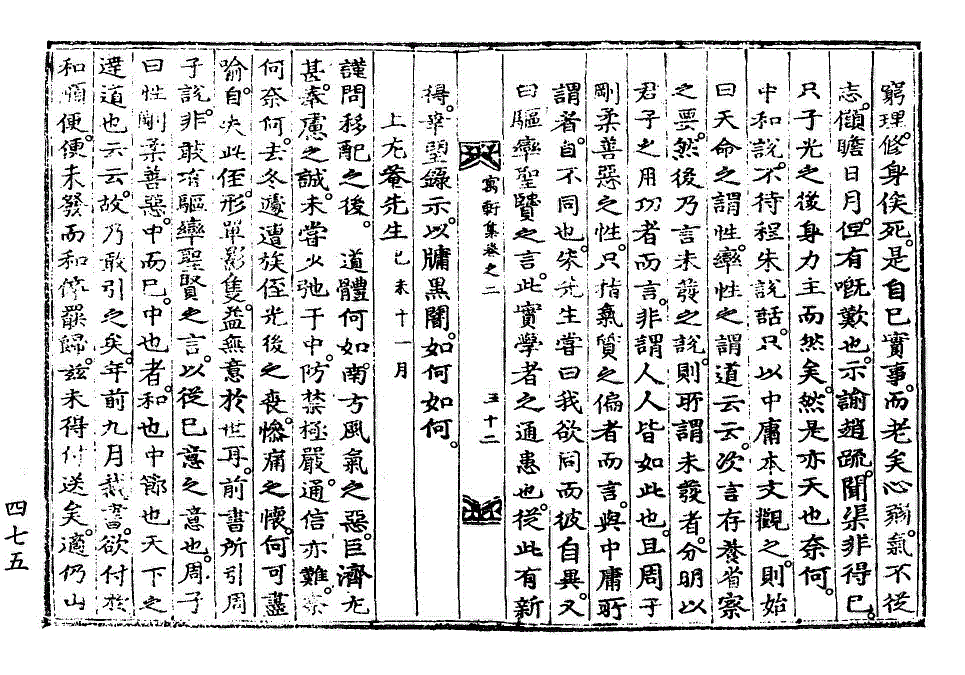 穷理。修身俟死。是自己实事。而老矣心弱。气不从志。顾瞻日月。但有嘅叹也。示谕赵疏。闻渠非得已。只子光之后身力主而然矣。然是亦天也奈何。
穷理。修身俟死。是自己实事。而老矣心弱。气不从志。顾瞻日月。但有嘅叹也。示谕赵疏。闻渠非得已。只子光之后身力主而然矣。然是亦天也奈何。中和说。不待程朱说话。只以中庸本文观之。则始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云云。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然后乃言未发之说。则所谓未发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功者而言。非谓人人皆如此也。且周子刚柔善恶之性。只指气质之偏者而言。与中庸所谓者。自不同也。朱先生尝曰我欲同而彼自异。又曰驱率圣贤之言。此实学者之通患也。从此有新得。幸望录示。以牖黑闇。如何如何。
上尤庵先生(己未十一月)
谨问移配之后。 道体何如。南方风气之恶。巨济尤甚。奉虑之诚。未尝少弛于中。防禁极严。通信亦难。奈何奈何。去冬遽遭族侄光后之丧。惨痛之怀。何可尽喻。自失此侄。形单影只。益无意于世耳。前书所引周子说。非敢有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之意也。周子曰性刚柔善恶。中而已。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云云。故乃敢引之矣。年前九月裁书。欲付于和顺便。便未发而和倅罢归。兹未得付送矣。适仍山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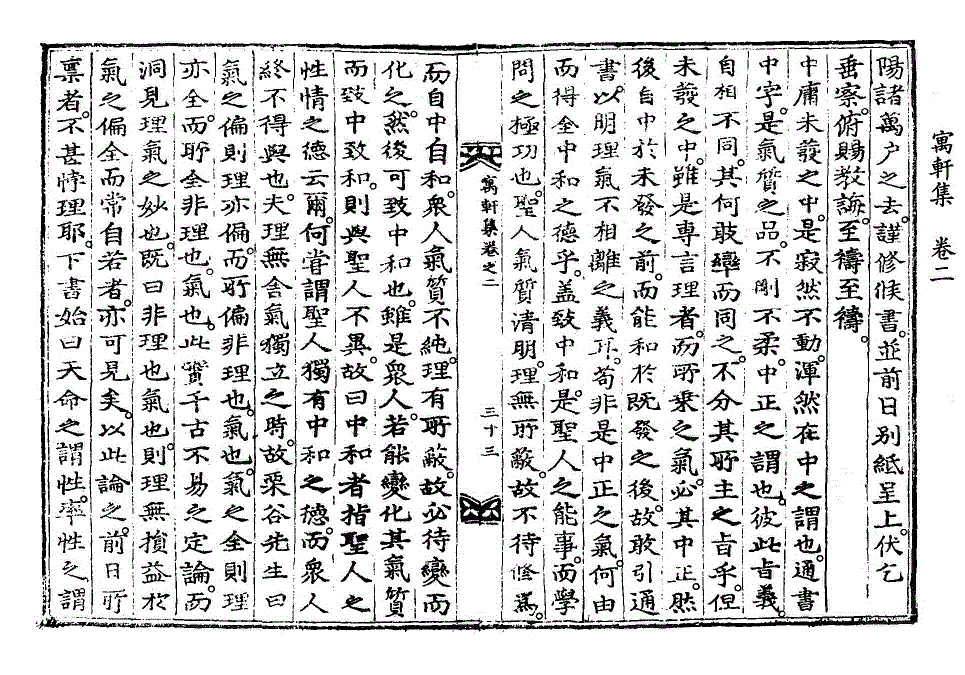 阳诸万户之去。谨修候书。并前日别纸呈上。伏乞 垂察。俯赐教诲。至祷至祷。
阳诸万户之去。谨修候书。并前日别纸呈上。伏乞 垂察。俯赐教诲。至祷至祷。中庸未发之中。是寂然不动。浑然在中之谓也。通书中字。是气质之品。不刚不柔。中正之谓也。彼此旨义。自相不同。其何敢率而同之。不分其所主之旨乎。但未发之中。虽是专言理者。而所乘之气。必其中正。然后自中于未发之前。而能和于既发之后。故敢引通书。以明理气不相离之义耳。苟非是中正之气。何由而得全中和之德乎。盖致中和。是圣人之能事。而学问之极功也。圣人气质清明。理无所蔽。故不待修为。而自中自和。众人气质不纯。理有所蔽。故必待变而化之。然后可致中和也。虽是众人。若能变化其气质而致中致和。则与圣人不异。故曰中和者指圣人之性情之德云尔。何尝谓圣人独有中和之德。而众人终不得与也。夫理无舍气独立之时。故栗谷先生曰气之偏则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气也。气之全则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气也。此实千古不易之定论。而洞见理气之妙也。既曰非理也气也。则理无损益于气之偏全而常自若者。亦可见矣。以此论之。前日所禀者。不甚悖理耶。下书始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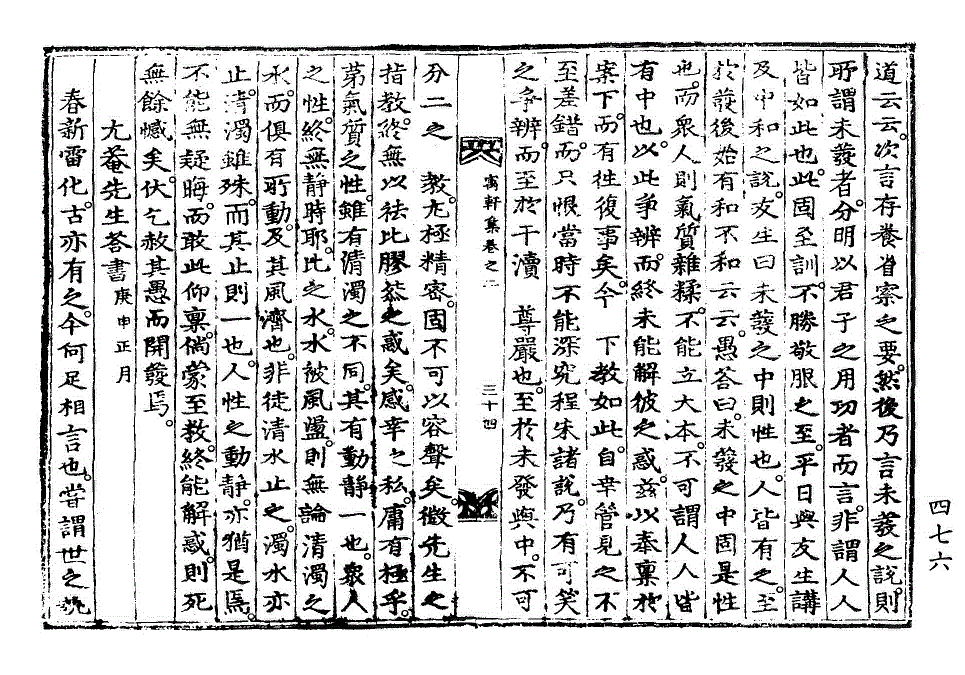 道云云。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然后乃言未发之说。则所谓未发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功者而言。非谓人人皆如此也。此固至训。不胜敬服之至。平日与友生讲及中和之说。友生曰未发之中则性也。人皆有之。至于发后始有和不和云云。愚答曰。未发之中固是性也。而众人则气质杂糅。不能立大本。不可谓人人皆有中也。以此争辨。而终未能解彼之惑。兹以奉禀于案下。而有往复事矣。今 下教如此。自幸管见之不至差错。而只恨当时不能深究程朱诸说。乃有可笑之争辨。而至于干渎 尊严也。至于未发与中。不可分二之 教。尤极精密。固不可以容声矣。微先生之指教。终无以祛比胶漆之惑矣。感幸之私。庸有极乎。第气质之性。虽有清浊之不同。其有动静一也。众人之性。终无静时耶。比之水。水被风荡。则无论清浊之水。而俱有所动。及其风济也。非徒清水止之。浊水亦止。清浊虽殊。而其止则一也。人性之动静。亦犹是焉。不能无疑晦。而敢此仰禀。倘蒙至教。终能解惑。则死无馀憾矣。伏乞赦其愚而开发焉。
道云云。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然后乃言未发之说。则所谓未发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功者而言。非谓人人皆如此也。此固至训。不胜敬服之至。平日与友生讲及中和之说。友生曰未发之中则性也。人皆有之。至于发后始有和不和云云。愚答曰。未发之中固是性也。而众人则气质杂糅。不能立大本。不可谓人人皆有中也。以此争辨。而终未能解彼之惑。兹以奉禀于案下。而有往复事矣。今 下教如此。自幸管见之不至差错。而只恨当时不能深究程朱诸说。乃有可笑之争辨。而至于干渎 尊严也。至于未发与中。不可分二之 教。尤极精密。固不可以容声矣。微先生之指教。终无以祛比胶漆之惑矣。感幸之私。庸有极乎。第气质之性。虽有清浊之不同。其有动静一也。众人之性。终无静时耶。比之水。水被风荡。则无论清浊之水。而俱有所动。及其风济也。非徒清水止之。浊水亦止。清浊虽殊。而其止则一也。人性之动静。亦犹是焉。不能无疑晦。而敢此仰禀。倘蒙至教。终能解惑。则死无馀憾矣。伏乞赦其愚而开发焉。尤庵先生答书(庚申正月)
春新雷化。古亦有之。今何足相言也。尝谓世之执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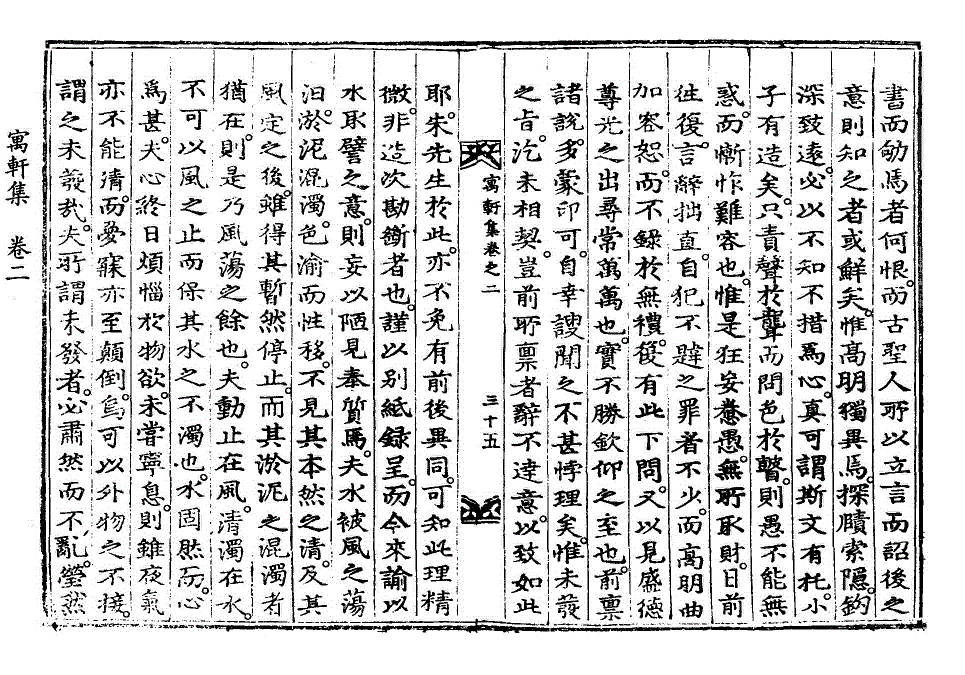 书而劬焉者何恨。而古圣人所以立言而诏后之意则知之者或鲜矣。惟高明独异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必以不知不措为心。真可谓斯文有托。小子有造矣。只责声于聋而问色于瞽。则愚不能无惑。而惭怍难容也。惟是狂妄憃愚。无所取财。日前往复。言辞拙直。自犯不韪之罪者不少。而高明曲加容恕。而不录于无礼。复有此下问。又以见盛德尊光之出寻常万万也。实不胜钦仰之至也。前禀诸说。多蒙印可。自幸謏闻之不甚悖理矣。惟未发之旨。汔未相契。岂前所禀者辞不达意。以致如此耶。朱先生于此。亦不免有前后异同。可知此理精微。非造次勘断者也。谨以别纸录呈。而今来谕以水取譬之意。则妄以陋见奉质焉。夫水被风之荡汨。淤泥混浊。色渝而性移。不见其本然之清。及其风定之后。虽得其暂然停止。而其淤泥之混浊者犹在。则是乃风荡之馀也。夫动止在风。清浊在水。不可以风之止而保其水之不浊也。水固然而。心为甚。夫心终日烦恼于物欲。未尝宁息。则虽夜气亦不能清。而梦寐亦至颠倒。乌可以外物之不接。谓之未发哉。夫所谓未发者。必肃然而不乱。莹然
书而劬焉者何恨。而古圣人所以立言而诏后之意则知之者或鲜矣。惟高明独异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必以不知不措为心。真可谓斯文有托。小子有造矣。只责声于聋而问色于瞽。则愚不能无惑。而惭怍难容也。惟是狂妄憃愚。无所取财。日前往复。言辞拙直。自犯不韪之罪者不少。而高明曲加容恕。而不录于无礼。复有此下问。又以见盛德尊光之出寻常万万也。实不胜钦仰之至也。前禀诸说。多蒙印可。自幸謏闻之不甚悖理矣。惟未发之旨。汔未相契。岂前所禀者辞不达意。以致如此耶。朱先生于此。亦不免有前后异同。可知此理精微。非造次勘断者也。谨以别纸录呈。而今来谕以水取譬之意。则妄以陋见奉质焉。夫水被风之荡汨。淤泥混浊。色渝而性移。不见其本然之清。及其风定之后。虽得其暂然停止。而其淤泥之混浊者犹在。则是乃风荡之馀也。夫动止在风。清浊在水。不可以风之止而保其水之不浊也。水固然而。心为甚。夫心终日烦恼于物欲。未尝宁息。则虽夜气亦不能清。而梦寐亦至颠倒。乌可以外物之不接。谓之未发哉。夫所谓未发者。必肃然而不乱。莹然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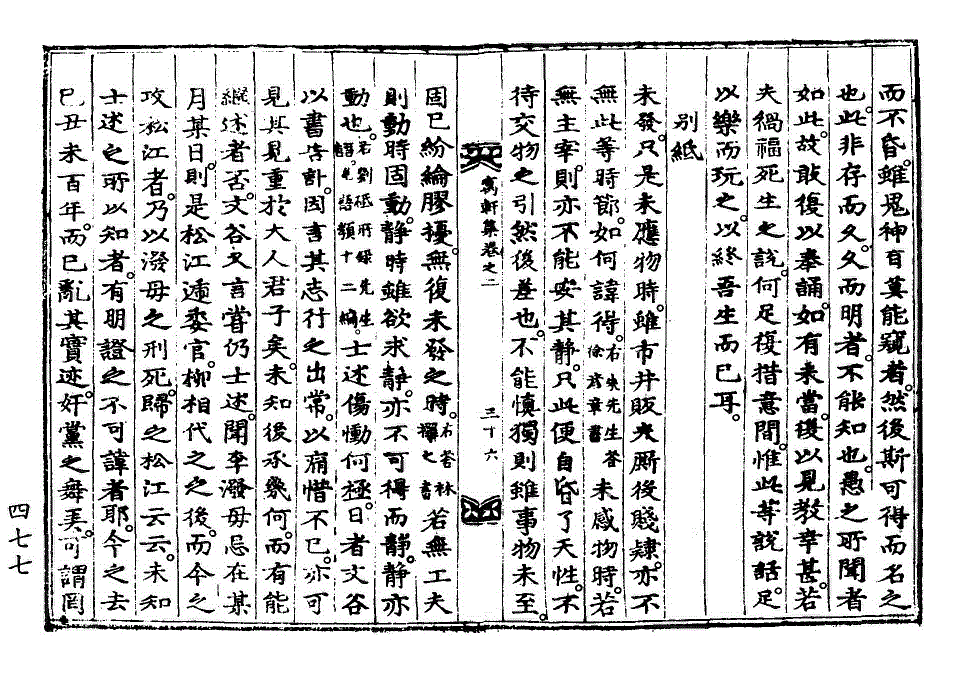 而不昏。虽鬼神有莫能窥者。然后斯可得而名之也。此非存而久。久而明者。不能知也。愚之所闻者如此。故敢复以奉诵。如有未当。复以见教幸甚。若夫祸福死生之说。何足复措意间。惟此等说话。足以乐而玩之。以终吾生而已耳。
而不昏。虽鬼神有莫能窥者。然后斯可得而名之也。此非存而久。久而明者。不能知也。愚之所闻者如此。故敢复以奉诵。如有未当。复以见教幸甚。若夫祸福死生之说。何足复措意间。惟此等说话。足以乐而玩之。以终吾生而已耳。别纸
未发。只是未应物时。虽市井贩夫厮役贱隶。亦不无此等时节。如何讳得。(右朱先生答徐彦章书)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后差也。不能慎独则虽事物未至。固已纷纶胶扰。无复未发之时。(右答林择之书)若无工夫则动时固动。静时虽欲求静。亦不可得而静。静亦动也。(右刘砥所录先生语。见语类十二编。)士述伤恸何极。日者文谷以书告讣。因言其志行之出常。以痛惜不已。亦可见其见重于大人君子矣。未知后承几何。而有能继述者否。文谷又言尝仍士述。闻李泼母忌在某月某日。则是松江递委官。柳相代之之后。而今之攻松江者。乃以泼母之刑死。归之松江云云。未知士述之所以知者。有明證之不可讳者耶。今之去己丑未百年。而已乱其实迹。奸党之舞弄。可谓罔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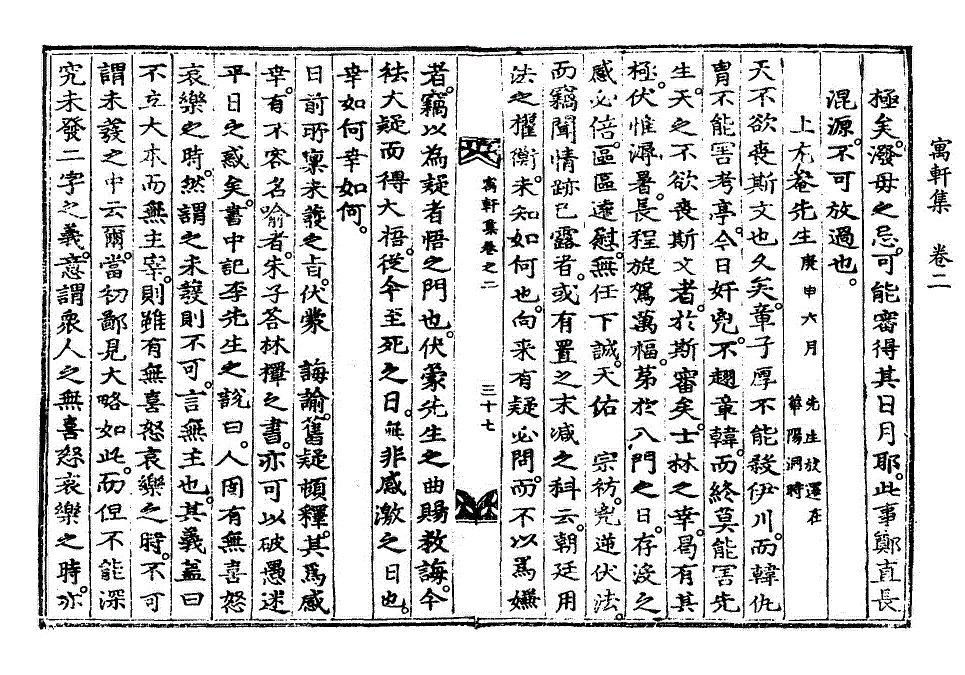 极矣。泼母之忌。可能审得其日月耶。此事郑直长混源。不可放过也。
极矣。泼母之忌。可能审得其日月耶。此事郑直长混源。不可放过也。上尤庵先生(庚申六月○先生放还在华阳洞时)
天不欲丧斯文也久矣。章子厚不能杀伊川。而韩侂胄不能害考亭。今日奸凶。不趐章韩。而终莫能害先生。天之不欲丧斯文者。于斯审矣。士林之幸。曷有其极。伏惟溽暑。长程旋驾万福。第于入门之日。存没之感必倍。区区远慰。无任下诚。天佑 宗祊。凶逆伏法。而窃闻情迹已露者。或有置之末减之科云。朝廷用法之权衡。未知如何也。向来有疑必问。而不以为嫌者。窃以为疑者悟之门也。伏蒙先生之曲赐教诲。今祛大疑而得大悟。从今至死之日。无非感激之日也。幸如何幸如何。
日前所禀未发之旨。伏蒙 诲谕。旧疑顿释。其为感幸。有不容名喻者。朱子答林择之书。亦可以破愚迷平日之惑矣。书中记李先生之说曰。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其义盖曰不立大本而无主宰。则虽有无喜怒哀乐之时。不可谓未发之中云尔。当初鄙见大略如此。而但不能深究未发二字之义。意谓众人之无喜怒哀乐之时。亦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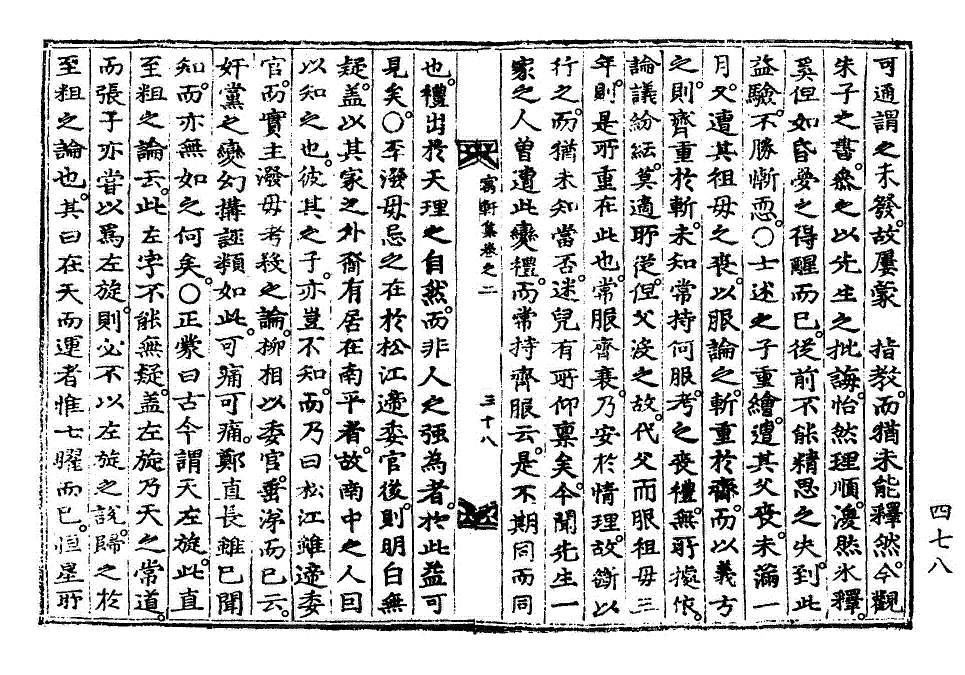 可通谓之未发。故屡蒙 指教。而犹未能释然。今观朱子之书。参之以先生之批诲。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奚但如昏梦之得醒而已。从前不能精思之失。到此益验。不胜惭恧。○士述之子重绘。遭其父丧。未满一月。又遭其祖母之丧。以服论之。斩重于齐。而以义方之。则齐重于斩。未知常持何服。考之丧礼。无所据依。论议纷纭。莫适所从。但父没之故。代父而服祖母三年。则是所重在此也。常服齐衰。乃安于情理。故断以行之。而犹未知当否。迷儿有所仰禀矣。今闻先生一家之人曾遭此变礼。而常持齐服云。是不期同而同也。礼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强为者。于此益可见矣。○李泼母忌之在于松江递委官后。则明白无疑。盖以其家之外裔有居在南平者。故南中之人因以知之也。彼其之子。亦岂不知。而乃曰松江虽递委官。而实主泼母考杀之论。柳相以委官。垂涕而已云。奸党之变幻搆诬类如此。可痛可痛。郑直长虽已闻知。而亦无如之何矣。○正蒙曰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云。此左字不能无疑。盖左旋乃天之常道。而张子亦尝以为左旋。则必不以左旋之说。归之于至粗之论也。其曰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
可通谓之未发。故屡蒙 指教。而犹未能释然。今观朱子之书。参之以先生之批诲。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奚但如昏梦之得醒而已。从前不能精思之失。到此益验。不胜惭恧。○士述之子重绘。遭其父丧。未满一月。又遭其祖母之丧。以服论之。斩重于齐。而以义方之。则齐重于斩。未知常持何服。考之丧礼。无所据依。论议纷纭。莫适所从。但父没之故。代父而服祖母三年。则是所重在此也。常服齐衰。乃安于情理。故断以行之。而犹未知当否。迷儿有所仰禀矣。今闻先生一家之人曾遭此变礼。而常持齐服云。是不期同而同也。礼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强为者。于此益可见矣。○李泼母忌之在于松江递委官后。则明白无疑。盖以其家之外裔有居在南平者。故南中之人因以知之也。彼其之子。亦岂不知。而乃曰松江虽递委官。而实主泼母考杀之论。柳相以委官。垂涕而已云。奸党之变幻搆诬类如此。可痛可痛。郑直长虽已闻知。而亦无如之何矣。○正蒙曰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云。此左字不能无疑。盖左旋乃天之常道。而张子亦尝以为左旋。则必不以左旋之说。归之于至粗之论也。其曰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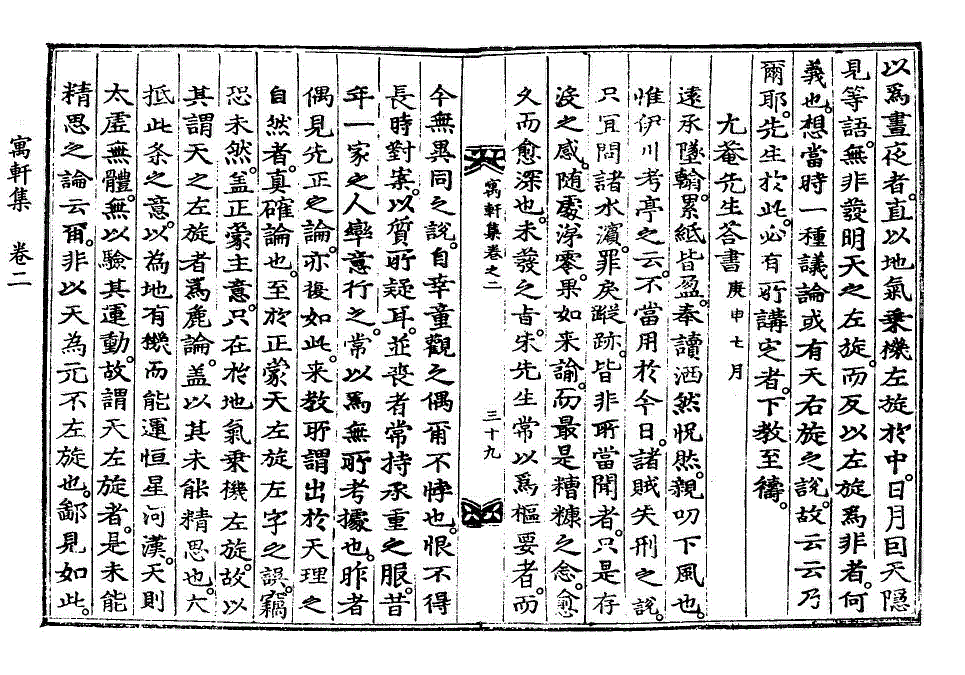 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左旋于中。日月因天隐见等语。无非发明天之左旋。而反以左旋为非者。何义也。想当时一种议论或有天右旋之说。故云云乃尔耶。先生于此。必有所讲定者。下教至祷。
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左旋于中。日月因天隐见等语。无非发明天之左旋。而反以左旋为非者。何义也。想当时一种议论或有天右旋之说。故云云乃尔耶。先生于此。必有所讲定者。下教至祷。尤庵先生答书(庚申七月)
远承坠翰。累纸皆盈。奉读洒然恍然。亲叨下风也。惟伊川考亭之云。不当用于今日。诸贼失刑之说。只宜问诸水滨。罪戾踪迹。皆非所当闻者。只是存没之感。随处涕零。果如来谕。而最是糟糠之念。愈久而愈深也。未发之旨。朱先生常以为枢要者。而今无异同之说。自幸童观之偶尔不悖也。恨不得长时对案。以质所疑耳。并丧者常持承重之服。昔年一家之人率意行之。常以焉无所考据也。昨者偶见先正之论。亦复如此。来教所谓出于天理之自然者。真确论也。至于正蒙天左旋左字之误。窃恐未然。盖正蒙主意。只在于地气乘机左旋。故以其谓天之左旋者为粗论。盖以其未能精思也。大抵此条之意。以为地有机而能运恒星河汉。天则太虚无体。无以验其运动。故谓天左旋者。是未能精思之论云尔。非以天为元不左旋也。鄙见如此。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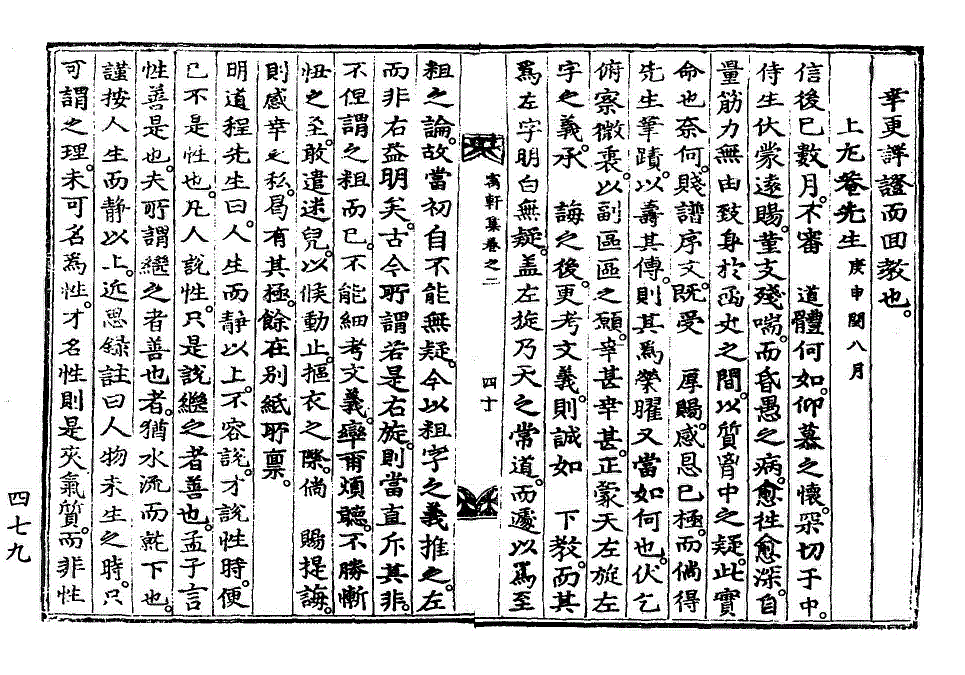 幸更详證而回教也。
幸更详證而回教也。上尤庵先生(庚申闰八月)
信后已数月。不审 道体何如。仰慕之怀。深切于中。侍生伏蒙远赐。堇支残喘。而昏愚之病。愈往愈深。自量筋力无由致身于亟丈之间。以质胸中之疑。此实命也奈何。贱谱序文。既受 厚赐。感恩已极。而倘得先生笔迹。以寿其传。则其为荣曜又当如何也。伏乞俯察微衷。以副区区之愿。幸甚幸甚。正蒙天左旋左字之义。承 诲之后。更考文义。则诚如 下教。而其为左字明白无疑。盖左旋乃天之常道。而遽以为至粗之论。故当初自不能无疑。今以粗字之义推之。左而非右益明矣。古今所谓若是右旋。则当直斥其非。不但谓之粗而已。不能细考文义。率尔烦听。不胜惭忸之至。敢遣迷儿。以候动止。抠衣之际。倘 赐提诲。则感幸之私。曷有其极。馀在别纸所禀。
明道程先生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谨按人生而静以上。近思录注曰人物未生之时。只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才名性则是夹气质。而非性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0H 页
 之本体云云。此说窃恐有违于程子之本旨矣。其曰人生而静。是未发之时也。以上。以前也。犹言未发之前也。不容说。谓性体至静。无迹可见。不可以容说也。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谓才谓之善则已涉于情。而非性也。以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观之。则所谓才说性云者。似是谓以善说性。而恐非谓名之以性也。若曰才名性。不是性云尔。则其文义实有使人难晓者矣。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记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云者。皆是人生以后。指其本体而名之以性。则程子何故于人生而静时。谓之非性也。盖性体难言而难名。故孟子不得已因其善端之发见。而道性以善。则其所谓善者。只是已发。而非性。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观其上下文义。则程子之意。只是性难容说。故云云乃尔。恐非谓人物未生之前也。至于程子并引大传孟子为说之义。则固无可疑者。盖天人一理。而初无彼此之殊。人性才发之始与天道流行之始。其义不异。故引之矣。如是观之则程夫子立言之旨。通畅明白。无所滞碍。而朱子答严时亨及欧阳希逊之问也。亦未能无疑于程子之言。而至以不可晓为答。
之本体云云。此说窃恐有违于程子之本旨矣。其曰人生而静。是未发之时也。以上。以前也。犹言未发之前也。不容说。谓性体至静。无迹可见。不可以容说也。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谓才谓之善则已涉于情。而非性也。以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观之。则所谓才说性云者。似是谓以善说性。而恐非谓名之以性也。若曰才名性。不是性云尔。则其文义实有使人难晓者矣。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记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云者。皆是人生以后。指其本体而名之以性。则程子何故于人生而静时。谓之非性也。盖性体难言而难名。故孟子不得已因其善端之发见。而道性以善。则其所谓善者。只是已发。而非性。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观其上下文义。则程子之意。只是性难容说。故云云乃尔。恐非谓人物未生之前也。至于程子并引大传孟子为说之义。则固无可疑者。盖天人一理。而初无彼此之殊。人性才发之始与天道流行之始。其义不异。故引之矣。如是观之则程夫子立言之旨。通畅明白。无所滞碍。而朱子答严时亨及欧阳希逊之问也。亦未能无疑于程子之言。而至以不可晓为答。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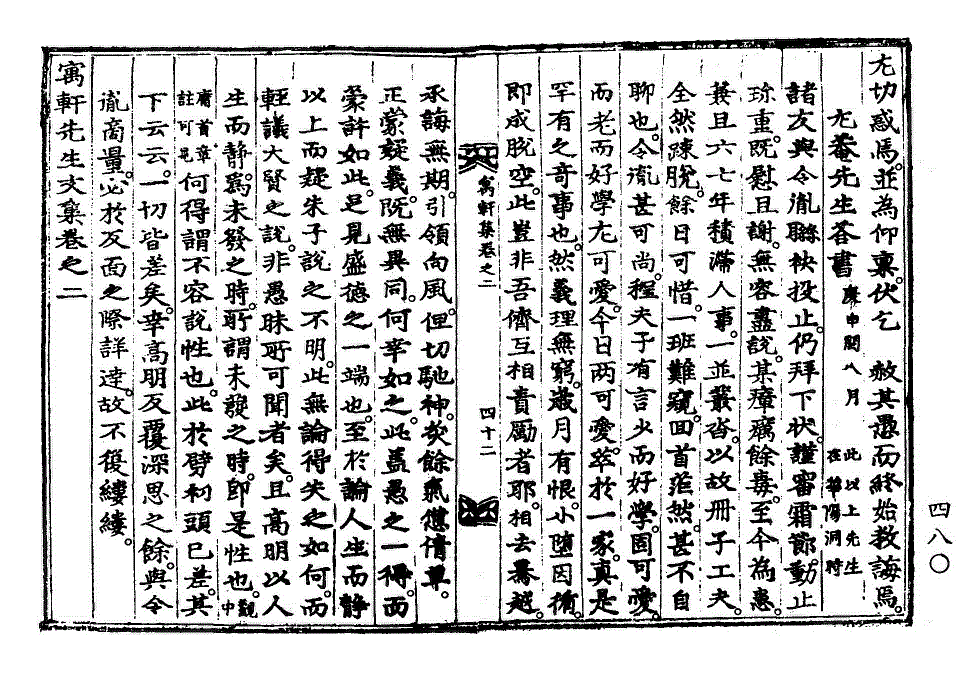 尤切惑焉。并为仰禀。伏乞 赦其愚而终始教诲焉。
尤切惑焉。并为仰禀。伏乞 赦其愚而终始教诲焉。尤庵先生答书(庚申闰八月○此以上先生在华阳洞时)
诸友与令胤联袂投止。仍拜下状。谨审霜节。动止珍重。既慰且谢。无容尽说。某瘴疠馀毒。至今为患。兼且六七年积滞人事。一并发沓。以故册子工夫。全然疏脱。馀日可惜。一班难窥。回首茫然。甚不自聊也。令胤甚可尚。程夫子有言少而好学。固可爱。而老而好学尤可爱。今日两可爱。萃于一家。真是罕有之奇事也。然义理无穷。岁月有恨。小堕因循。即成脱空。此岂非吾侪互相责励者耶。相去蓦越。承诲无期。引领向风。但切驰神。灸馀气惫倩草。
正蒙疑义。既无异同。何幸如之。此盖愚之一得。而蒙许如此。足见盛德之一端也。至于论人生而静以上而疑朱子说之不明。此无论得失之如何。而轻议大贤之说。非愚昧所可闻者矣。且高明以人生而静。为未发之时。所谓未发之时。即是性也。(观中庸首章注可见)何得谓不容说性也。此于劈初头已差。其下云云。一切皆差矣。幸高明反覆深思之馀。与令胤啇量。必于反面之际详达。故不复缕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