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杂著
杂著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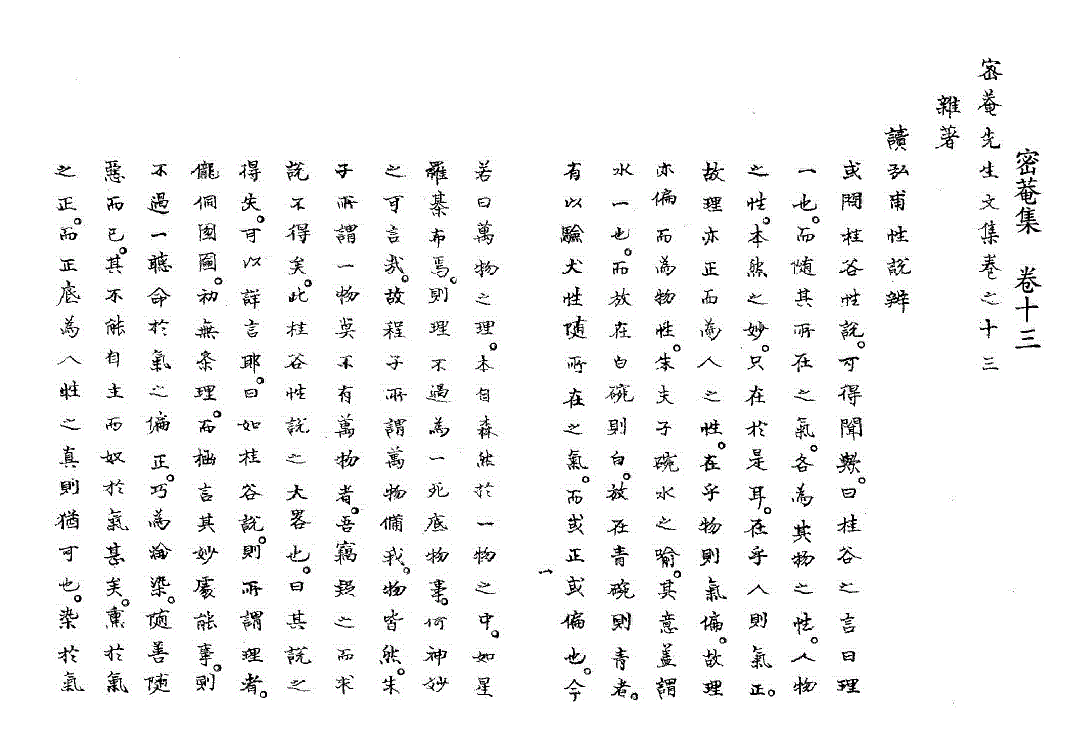 读弘甫性说辨
读弘甫性说辨或问桂谷性说。可得闻欤。曰桂谷之言曰理一也。而随其所在之气。各为其物之性。人物之性。本然之妙。只在于是耳。在乎人则气正。故理亦正而为人之性。在乎物则气偏。故理亦偏而为物性。朱夫子碗水之喻。其意盖谓水一也。而放在白碗则白。放在青碗则青者。有以验犬性随所在之气。而或正或偏也。今若曰万物之理。本自森然于一物之中。如星罗棋布焉。则理不过为一死底物事。何神妙之可言哉。故程子所谓万物备我。物皆然。朱子所谓一物莫不有万物者。吾窃疑之而求说不得矣。此桂谷性说之大略也。曰其说之得失。可以详言耶。曰如桂谷说。则所谓理者。儱侗囫囵。初无条理。而极言其妙处能事。则不过一听命于气之偏正。巧为沦染。随善随恶而已。其不能自主而奴于气甚矣。熏于气之正。而正底为人牲(一作性)之真则犹可也。染于气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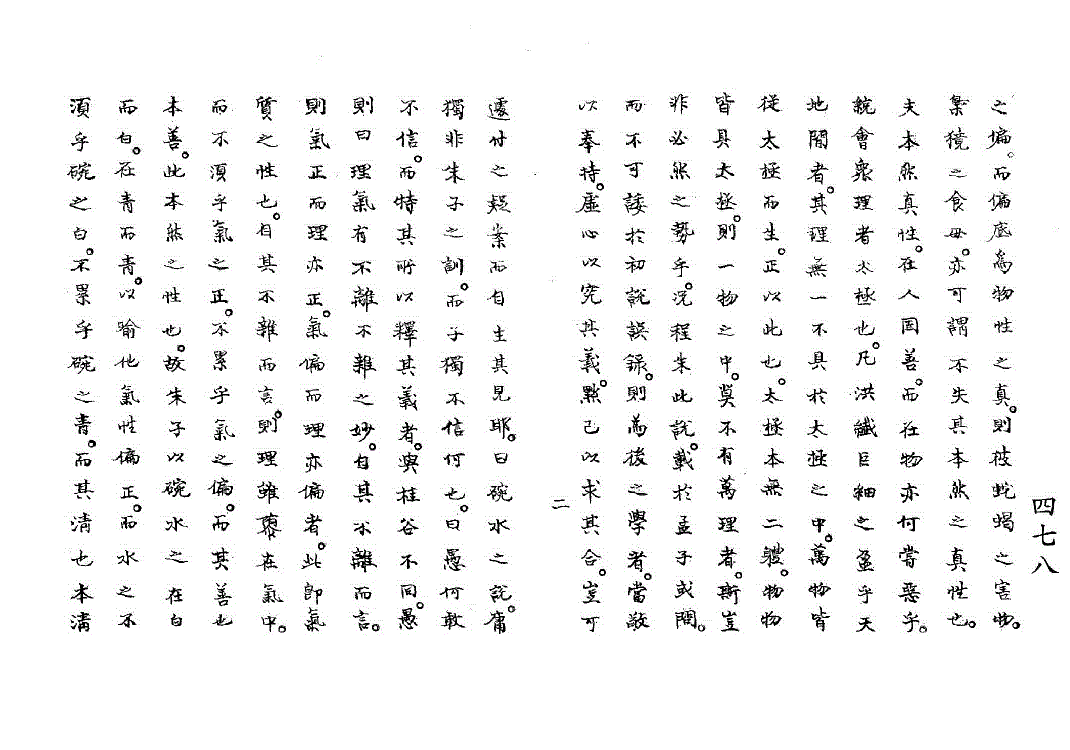 之偏。而偏底为物性之真。则彼蛇蝎之害物。枭獍之食母。亦可谓不失其本然之真性也。夫本然真性。在人固善。而在物亦何尝恶乎。统会众理者太极也。凡洪纤巨细之盈乎天地间者。其理无一不具于太极之中。万物皆从太极而生。正以此也。太极本无二体。物物皆具太极。则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理者。斯岂非必然之势乎。况程朱此说。载于孟子或问。而不可诿于初说误录。则为后之学者。当敬以奉持。虚心以究其义。黜己以求其合。岂可遽付之疑案而自主其见耶。曰碗水之说。庸独非朱子之训。而子独不信何也。曰愚何敢不信。而特其所以释其义者。与桂谷不同。愚则曰理气有不离不杂之妙。自其不离而言。则气正而理亦正。气偏而理亦偏者。此即气质之性也。自其不杂而言。则理虽隳在气中。而不须乎气之正。不累乎气之偏。而其善也本善。此本然之性也。故朱子以碗水之在白而白。在青而青。以喻他气性偏正。而水之不须乎碗之白。不累乎碗之青。而其清也本清
之偏。而偏底为物性之真。则彼蛇蝎之害物。枭獍之食母。亦可谓不失其本然之真性也。夫本然真性。在人固善。而在物亦何尝恶乎。统会众理者太极也。凡洪纤巨细之盈乎天地间者。其理无一不具于太极之中。万物皆从太极而生。正以此也。太极本无二体。物物皆具太极。则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理者。斯岂非必然之势乎。况程朱此说。载于孟子或问。而不可诿于初说误录。则为后之学者。当敬以奉持。虚心以究其义。黜己以求其合。岂可遽付之疑案而自主其见耶。曰碗水之说。庸独非朱子之训。而子独不信何也。曰愚何敢不信。而特其所以释其义者。与桂谷不同。愚则曰理气有不离不杂之妙。自其不离而言。则气正而理亦正。气偏而理亦偏者。此即气质之性也。自其不杂而言。则理虽隳在气中。而不须乎气之正。不累乎气之偏。而其善也本善。此本然之性也。故朱子以碗水之在白而白。在青而青。以喻他气性偏正。而水之不须乎碗之白。不累乎碗之青。而其清也本清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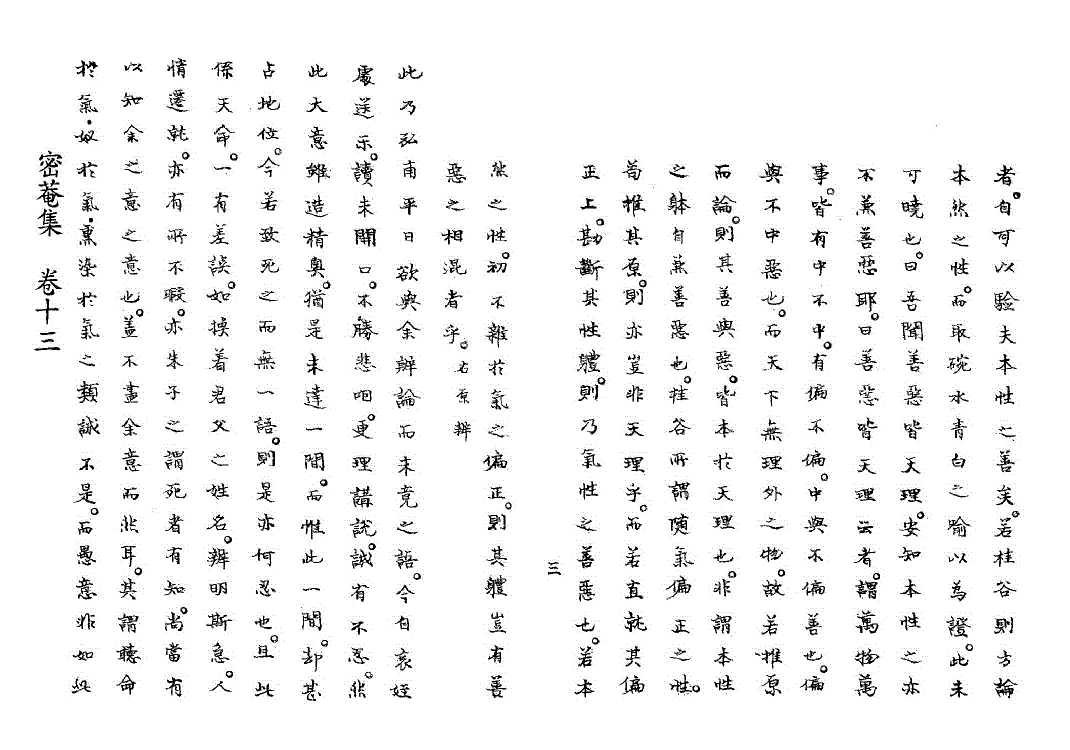 者。自可以验夫本性之善矣。若桂谷则方论本然之性。而取碗水青白之喻以为證。此未可晓也。曰吾闻善恶皆天理。安知本性之亦不兼善恶耶。曰善恶皆天理云者。谓万物万事。皆有中不中。有偏不偏。中与不偏善也。偏与不中恶也。而天下无理外之物。故若推原而论。则其善与恶。皆本于天理也。非谓本性之体自兼善恶也。桂谷所谓随气偏正之性。苟推其原。则亦岂非天理乎。而若直就其偏正上。勘断其性体。则乃气性之善恶也。若本然之性。初不杂于气之偏正。则其体岂有善恶之相混者乎。(右原辨)
者。自可以验夫本性之善矣。若桂谷则方论本然之性。而取碗水青白之喻以为證。此未可晓也。曰吾闻善恶皆天理。安知本性之亦不兼善恶耶。曰善恶皆天理云者。谓万物万事。皆有中不中。有偏不偏。中与不偏善也。偏与不中恶也。而天下无理外之物。故若推原而论。则其善与恶。皆本于天理也。非谓本性之体自兼善恶也。桂谷所谓随气偏正之性。苟推其原。则亦岂非天理乎。而若直就其偏正上。勘断其性体。则乃气性之善恶也。若本然之性。初不杂于气之偏正。则其体岂有善恶之相混者乎。(右原辨)此乃弘甫平日欲与余辨论而未竟之语。今自哀侄处送示。读未开口。不胜悲咽。更理讲说。诚有不忍。然此大意虽造精奥。犹是未达一间。而惟此一间。却甚占地位。今若致死之而无一语。则是亦何忍也。且此系天命。一有差误。如换着君父之姓名。辨明斯急。人情迁就。亦有所不暇。亦朱子之谓死者有知。尚当有以知余之意之意也。盖不尽余意而然耳。其谓听命于气,奴于气,熏染于气之类诚不是。而愚意非如此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79L 页
 也。本然有偏正则诚不是。而亦愚意非如此也。其不尽吾意既如此。则是不曾领会到吾所言之境界也。其谓理无一不具于太极之中。万物皆从太极而生。太极本无二体。物物皆具太极云者。皆是真宲题目也。然其所主之义。乃又曰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理云。则其真宲之题目。乃亦只是依前人言语而未见真得到宲然之地也。盖其以太极之具万理。而物物皆具太极。为一物中有万理者。以其语则似矣。究其宲则以一物具万理。却无来脉。既曰万理。则是万物之理也。既是万物之理。则正是万物之理也。安得为一物之所具。而若果以一物而可具。则即又是一物之理也。初安得有万理之名也。若其所谓万者。只如人是一物。而具有耳目聪明。父子慈孝之类。各具其物中之万理则可。若使人是一物。而其中又具狗彘嗜粪秽。草木冥无觉之理。犬是一物。而又具人之仁智。牛马龁草耕载之万理则可乎。名宲之间。互相舛戾。言语不顺。理致不成。万物性同。万性一性之意。岂或如是。而乃谓一物具万物之性哉。诚不知太极之所以具万物者。为如何体段。而乃于一物之中。得有万理耶。苟其真知太极之所以具万理。与万物之所以
也。本然有偏正则诚不是。而亦愚意非如此也。其不尽吾意既如此。则是不曾领会到吾所言之境界也。其谓理无一不具于太极之中。万物皆从太极而生。太极本无二体。物物皆具太极云者。皆是真宲题目也。然其所主之义。乃又曰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理云。则其真宲之题目。乃亦只是依前人言语而未见真得到宲然之地也。盖其以太极之具万理。而物物皆具太极。为一物中有万理者。以其语则似矣。究其宲则以一物具万理。却无来脉。既曰万理。则是万物之理也。既是万物之理。则正是万物之理也。安得为一物之所具。而若果以一物而可具。则即又是一物之理也。初安得有万理之名也。若其所谓万者。只如人是一物。而具有耳目聪明。父子慈孝之类。各具其物中之万理则可。若使人是一物。而其中又具狗彘嗜粪秽。草木冥无觉之理。犬是一物。而又具人之仁智。牛马龁草耕载之万理则可乎。名宲之间。互相舛戾。言语不顺。理致不成。万物性同。万性一性之意。岂或如是。而乃谓一物具万物之性哉。诚不知太极之所以具万物者。为如何体段。而乃于一物之中。得有万理耶。苟其真知太极之所以具万理。与万物之所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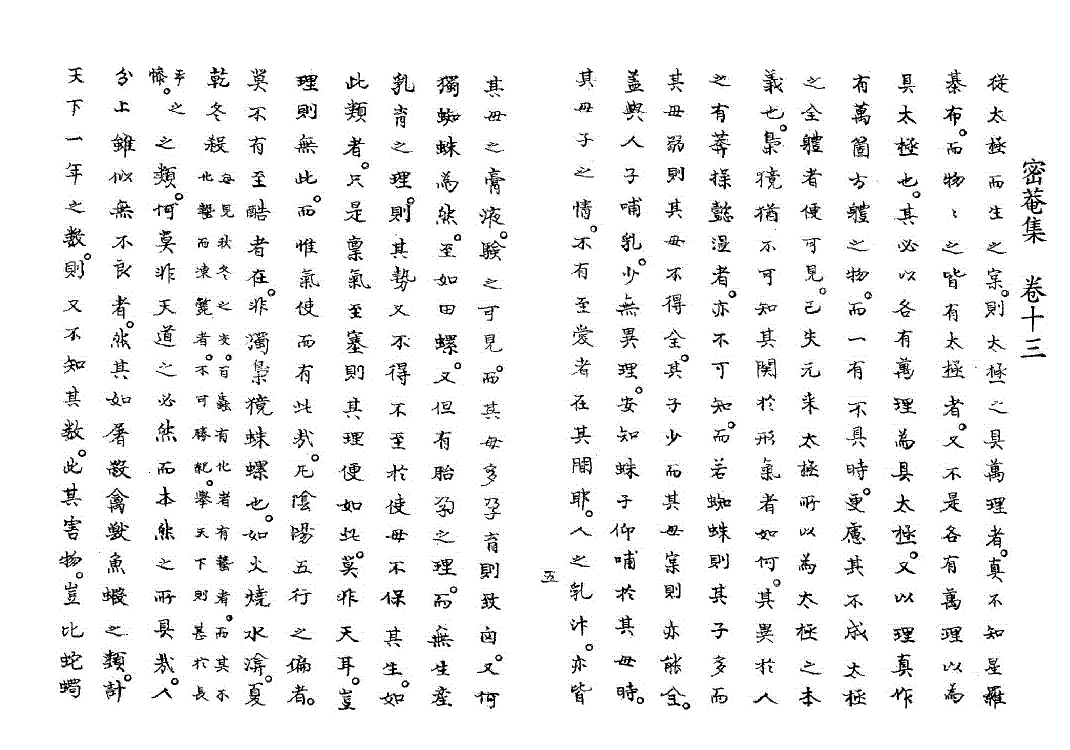 从太极而生之宲。则太极之具万理者。真不知星罗棋布。而物物之皆有太极者。又不是各有万理以为具太极也。其必以各有万理为具太极。又以理真作有万个方体之物。而一有不具时。更虑其不成太极之全体者便可见。已失元来太极所以为太极之本义也。枭獍犹不可知其关于形气者如何。其异于人之有莽操懿温者。亦不可知。而若蜘蛛则其子多而其母弱则其母不得全。其子少而其母宲则亦能全。盖与人子哺乳。少无异理。安知蛛子仰哺于其母时。其母子之情。不有至爱者在其间耶。人之乳汁。亦皆其母之膏液。验之可见。而其母多孕育则致凶。又何独蜘蛛为然。至如田螺。又但有胎孕之理。而无生产乳育之理。则其势又不得不至于使母不保其生。如此类者。只是禀气至塞则其理便如此。莫非天耳。岂理则无此。而惟气使而有此哉。凡阴阳五行之偏者。莫不有至酷者在。非独枭獍蛛螺也。如火烧水渰。夏乾冬杀(每见秋冬之交。百虫有化者有蛰者。而其不化蛰而冻毙者。不可胜纪。举天下则甚于长平之惨。)之类。何莫非天道之必然而本然之所具哉。人分上虽似无不良者。然其如屠杀禽兽鱼虾之类。计天下一年之数。则又不知其数。此其害物。岂比蛇蝎
从太极而生之宲。则太极之具万理者。真不知星罗棋布。而物物之皆有太极者。又不是各有万理以为具太极也。其必以各有万理为具太极。又以理真作有万个方体之物。而一有不具时。更虑其不成太极之全体者便可见。已失元来太极所以为太极之本义也。枭獍犹不可知其关于形气者如何。其异于人之有莽操懿温者。亦不可知。而若蜘蛛则其子多而其母弱则其母不得全。其子少而其母宲则亦能全。盖与人子哺乳。少无异理。安知蛛子仰哺于其母时。其母子之情。不有至爱者在其间耶。人之乳汁。亦皆其母之膏液。验之可见。而其母多孕育则致凶。又何独蜘蛛为然。至如田螺。又但有胎孕之理。而无生产乳育之理。则其势又不得不至于使母不保其生。如此类者。只是禀气至塞则其理便如此。莫非天耳。岂理则无此。而惟气使而有此哉。凡阴阳五行之偏者。莫不有至酷者在。非独枭獍蛛螺也。如火烧水渰。夏乾冬杀(每见秋冬之交。百虫有化者有蛰者。而其不化蛰而冻毙者。不可胜纪。举天下则甚于长平之惨。)之类。何莫非天道之必然而本然之所具哉。人分上虽似无不良者。然其如屠杀禽兽鱼虾之类。计天下一年之数。则又不知其数。此其害物。岂比蛇蝎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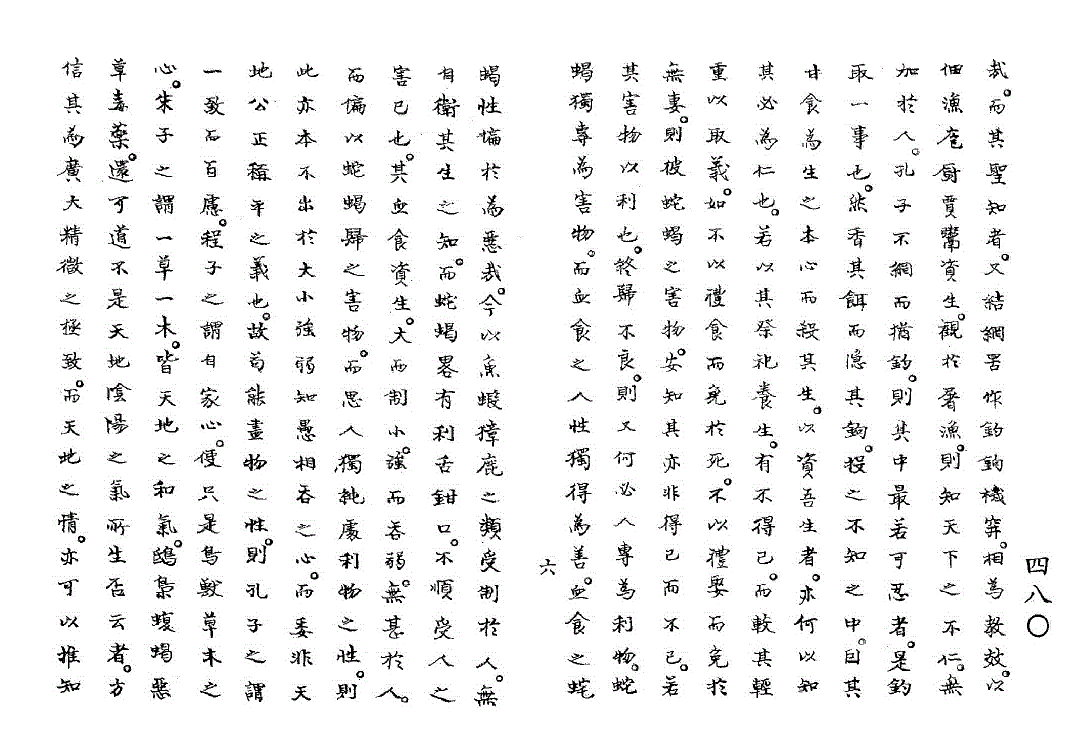 哉。而其圣知者。又结网罟作钓钩机阱。相为教效。以佃渔庖厨贾鬻资生。观于屠渔。则知天下之不仁。无加于人。孔子不网而犹钓。则其中最若可忍者。是钓取一事也。然香其饵而隐其钩。投之不知之中。因其甘食为生之本心而杀其生。以资吾生者。亦何以知其必为仁也。若以其祭祀养生。有不得已。而较其轻重以取义。如不以礼食而免于死。不以礼娶而免于无妻。则彼蛇蝎之害物。安知其亦非得已而不已。若其害物以利也。终归不良。则又何必人专为利物。蛇蝎独专为害物。而血食之人性独得为善。血食之䖳(一作蛇)蝎性偏于为恶哉。今以鱼虾獐鹿之类受制于人。无自卫其生之知。而蛇蝎略有利舌钳口。不顺受人之害己也。其血食资生。大而制小。强而吞弱。无甚于人。而偏以蛇蝎归之害物。而思人独纯处利物之性。则此亦本不出于大小强弱知愚相吞之心。而委非天地公正称平之义也。故苟能尽物之性。则孔子之谓一致而百虑。程子之谓自家心。便只是鸟兽草木之心。朱子之谓一草一木。皆天地之和气。䲭枭蝮蝎恶草毒药。还可道不是天地阴阳之气所生否云者。方信其为广大精微之极致。而天地之情。亦可以推知
哉。而其圣知者。又结网罟作钓钩机阱。相为教效。以佃渔庖厨贾鬻资生。观于屠渔。则知天下之不仁。无加于人。孔子不网而犹钓。则其中最若可忍者。是钓取一事也。然香其饵而隐其钩。投之不知之中。因其甘食为生之本心而杀其生。以资吾生者。亦何以知其必为仁也。若以其祭祀养生。有不得已。而较其轻重以取义。如不以礼食而免于死。不以礼娶而免于无妻。则彼蛇蝎之害物。安知其亦非得已而不已。若其害物以利也。终归不良。则又何必人专为利物。蛇蝎独专为害物。而血食之人性独得为善。血食之䖳(一作蛇)蝎性偏于为恶哉。今以鱼虾獐鹿之类受制于人。无自卫其生之知。而蛇蝎略有利舌钳口。不顺受人之害己也。其血食资生。大而制小。强而吞弱。无甚于人。而偏以蛇蝎归之害物。而思人独纯处利物之性。则此亦本不出于大小强弱知愚相吞之心。而委非天地公正称平之义也。故苟能尽物之性。则孔子之谓一致而百虑。程子之谓自家心。便只是鸟兽草木之心。朱子之谓一草一木。皆天地之和气。䲭枭蝮蝎恶草毒药。还可道不是天地阴阳之气所生否云者。方信其为广大精微之极致。而天地之情。亦可以推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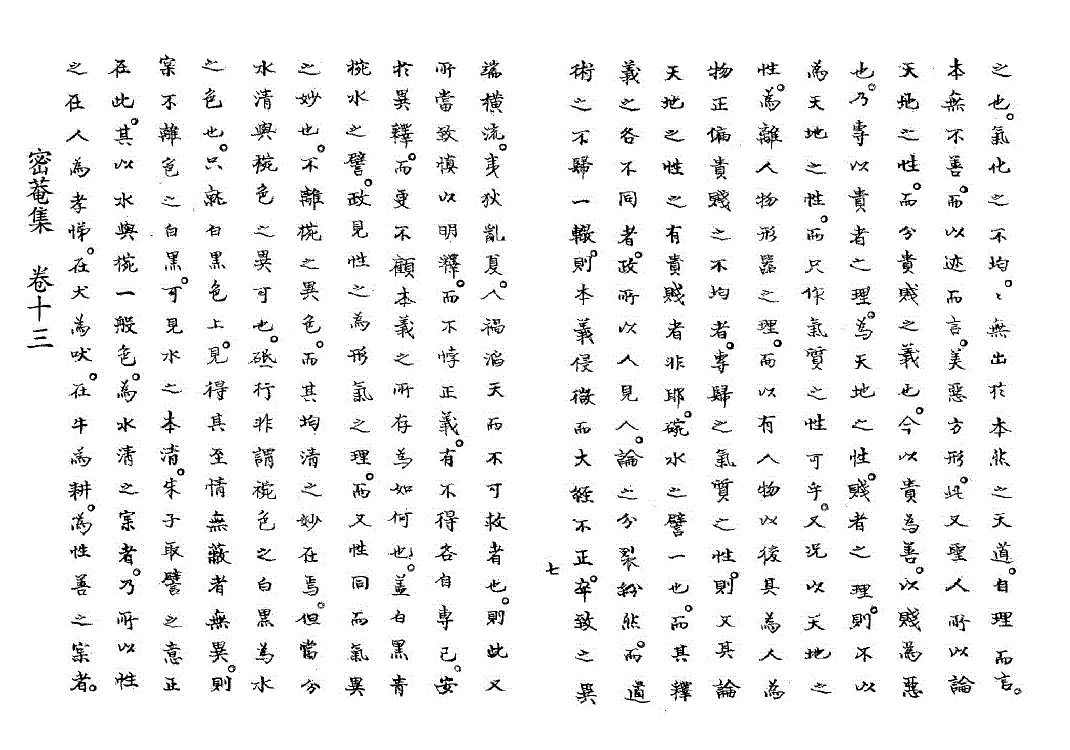 之也。气化之不均。均无出于本然之天道。自理而言。本无不善。而以迹而言。美恶方形。此又圣人所以论天地之性。而分贵贱之义也。今以贵为善。以贱为恶也。乃专以贵者之理。为天地之性。贱者之理。则不以为天地之性。而只作气质之性可乎。又况以天地之性。为离人物形器之理。而以有人物以后其为人为物正偏贵贱之不均者。专归之气质之性。则又其论天地之性之有贵贱者非耶。碗水之譬一也。而其释义之各不同者。政所以人见人。论之分裂纷然。而道术之不归一辙。则本义侵微而大经不正。卒致之异端横流。夷狄乱夏。人祸滔天而不可救者也。则此又所当致慎以明释。而不悖正义。有不得各自专己。安于异释。而更不顾本义之所存为如何也。盖白黑青碗水之譬。政见性之为形气之理。而又性同而气异之妙也。不离碗之异色。而其均清之妙在焉。但当分水清与碗色之异可也。砥行非谓碗色之白黑为水之色也。只就白黑色上。见得其至情无蔽者无异。则宲不离色之白黑。可见水之本清。朱子取譬之意正在此。其以水与碗一般色。为水清之宲者。乃所以性之在人为孝悌。在犬为吠。在牛为耕。为性善之宲者。
之也。气化之不均。均无出于本然之天道。自理而言。本无不善。而以迹而言。美恶方形。此又圣人所以论天地之性。而分贵贱之义也。今以贵为善。以贱为恶也。乃专以贵者之理。为天地之性。贱者之理。则不以为天地之性。而只作气质之性可乎。又况以天地之性。为离人物形器之理。而以有人物以后其为人为物正偏贵贱之不均者。专归之气质之性。则又其论天地之性之有贵贱者非耶。碗水之譬一也。而其释义之各不同者。政所以人见人。论之分裂纷然。而道术之不归一辙。则本义侵微而大经不正。卒致之异端横流。夷狄乱夏。人祸滔天而不可救者也。则此又所当致慎以明释。而不悖正义。有不得各自专己。安于异释。而更不顾本义之所存为如何也。盖白黑青碗水之譬。政见性之为形气之理。而又性同而气异之妙也。不离碗之异色。而其均清之妙在焉。但当分水清与碗色之异可也。砥行非谓碗色之白黑为水之色也。只就白黑色上。见得其至情无蔽者无异。则宲不离色之白黑。可见水之本清。朱子取譬之意正在此。其以水与碗一般色。为水清之宲者。乃所以性之在人为孝悌。在犬为吠。在牛为耕。为性善之宲者。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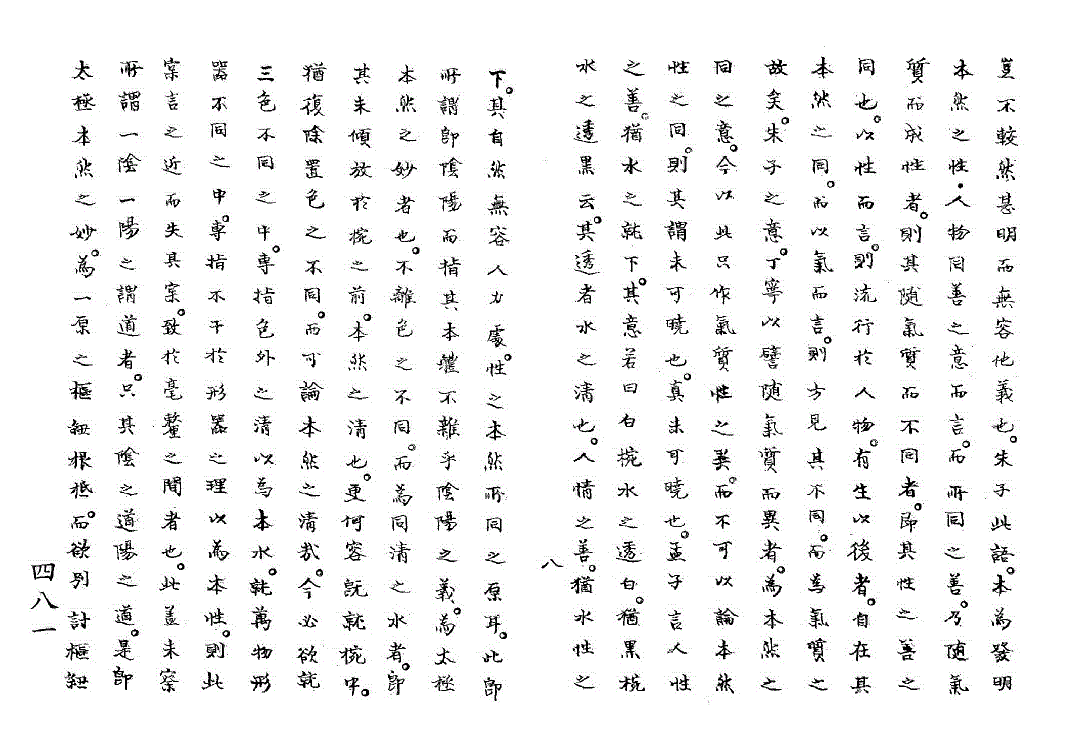 岂不较然甚明而无容他义也。朱子此语。本为发明本然之性,人物同善之意而言。而所同之善。乃随气质而成性者。则其随气质而不同者。即其性之善之同也。以性而言。则流行于人物。有生以后者。自在其本然之同。而以气而言。则方见其不同。而为气质之故矣。朱子之意。丁宁以譬随气质而异者。为本然之同之意。今以此只作气质性之异。而不可以论本然性之同。则其谓未可晓也。真未可晓也。孟子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其意若曰白碗水之透白。犹黑碗水之透黑云。其透者水之清也。人情之善。犹水性之下。其自然无容人力处。性之本然所同之原耳。此即所谓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之义。为太极本然之妙者也。不离色之不同。而为同清之水者。即其未倾放于碗之前。本然之清也。更何容既就碗中。犹复除置色之不同。而可论本然之清哉。今必欲就三色不同之中。专指色外之清以为本水。就万物形器不同之中。专指不干于形器之理以为本性。则此宲言之近而失其宲。致于毫釐之间者也。此盖未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只其阴之道阳之道。是即太极本然之妙。为一原之枢纽根柢。而欲别讨枢纽
岂不较然甚明而无容他义也。朱子此语。本为发明本然之性,人物同善之意而言。而所同之善。乃随气质而成性者。则其随气质而不同者。即其性之善之同也。以性而言。则流行于人物。有生以后者。自在其本然之同。而以气而言。则方见其不同。而为气质之故矣。朱子之意。丁宁以譬随气质而异者。为本然之同之意。今以此只作气质性之异。而不可以论本然性之同。则其谓未可晓也。真未可晓也。孟子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其意若曰白碗水之透白。犹黑碗水之透黑云。其透者水之清也。人情之善。犹水性之下。其自然无容人力处。性之本然所同之原耳。此即所谓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之义。为太极本然之妙者也。不离色之不同。而为同清之水者。即其未倾放于碗之前。本然之清也。更何容既就碗中。犹复除置色之不同。而可论本然之清哉。今必欲就三色不同之中。专指色外之清以为本水。就万物形器不同之中。专指不干于形器之理以为本性。则此宲言之近而失其宲。致于毫釐之间者也。此盖未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只其阴之道阳之道。是即太极本然之妙。为一原之枢纽根柢。而欲别讨枢纽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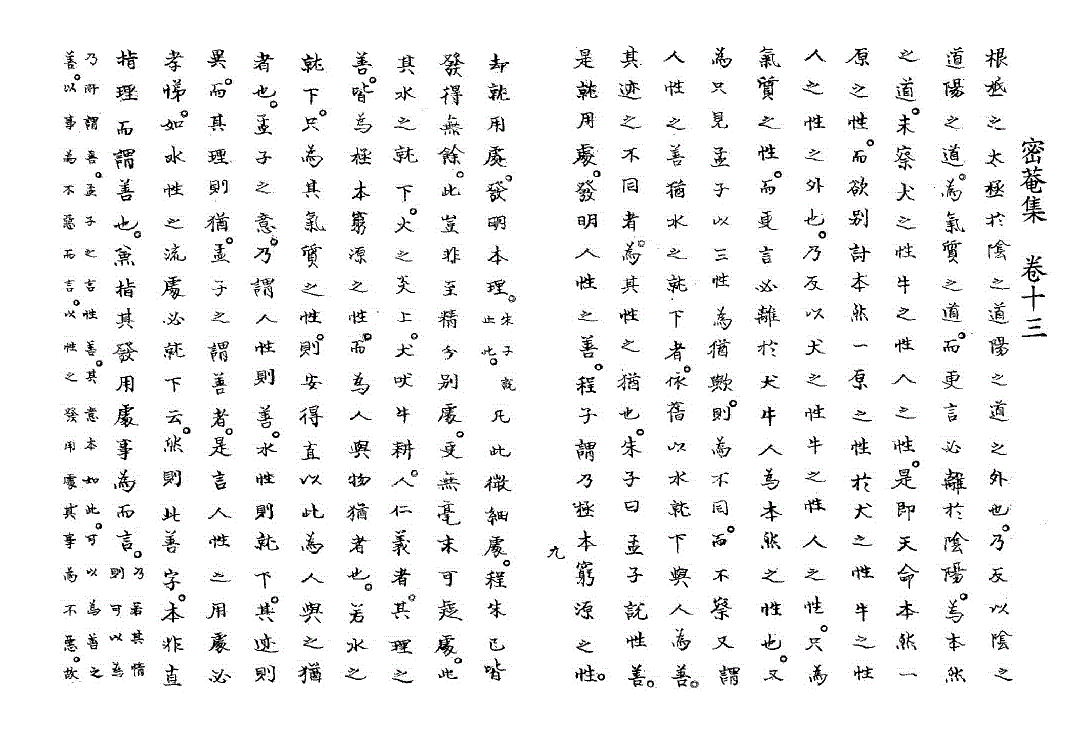 根柢之太极于阴之道阳之道之外也。乃反以阴之道阳之道。为气质之道。而更言必离于阴阳。为本然之道。未察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是即天命本然一原之性。而欲别讨本然一原之性于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外也。乃反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只为气质之性。而更言必离于犬牛人为本然之性也。又为只见孟子以三性为犹欤。则为不同。而不察又谓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者。依旧以水就下与人为善。其迹之不同者。为其性之犹也。朱子曰孟子说性善。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谓乃极本穷源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朱子说止此。)凡此微细处。程朱已皆发得无馀。此岂非至精分别处。更无毫末可疑处。此其水之就下。火之炎上。犬吠牛耕。人仁义者。其理之善。皆为极本穷源之性。而为人与物犹者也。若水之就下。只为其气质之性。则安得直以此为人与之犹者也。孟子之意。乃谓人性则善。水性则就下。其迹则异。而其理则犹。孟子之谓善者。是言人性之用处必孝悌。如水性之流处必就下云。然则此善字。本非直指理而谓善也。兼指其发用处事为而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乃所谓善。孟子之言性善。其意本如此。可以为善之善。以事为不恶而言。以性之发用处其事为不恶。故
根柢之太极于阴之道阳之道之外也。乃反以阴之道阳之道。为气质之道。而更言必离于阴阳。为本然之道。未察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是即天命本然一原之性。而欲别讨本然一原之性于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外也。乃反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只为气质之性。而更言必离于犬牛人为本然之性也。又为只见孟子以三性为犹欤。则为不同。而不察又谓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者。依旧以水就下与人为善。其迹之不同者。为其性之犹也。朱子曰孟子说性善。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谓乃极本穷源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朱子说止此。)凡此微细处。程朱已皆发得无馀。此岂非至精分别处。更无毫末可疑处。此其水之就下。火之炎上。犬吠牛耕。人仁义者。其理之善。皆为极本穷源之性。而为人与物犹者也。若水之就下。只为其气质之性。则安得直以此为人与之犹者也。孟子之意。乃谓人性则善。水性则就下。其迹则异。而其理则犹。孟子之谓善者。是言人性之用处必孝悌。如水性之流处必就下云。然则此善字。本非直指理而谓善也。兼指其发用处事为而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乃所谓善。孟子之言性善。其意本如此。可以为善之善。以事为不恶而言。以性之发用处其事为不恶。故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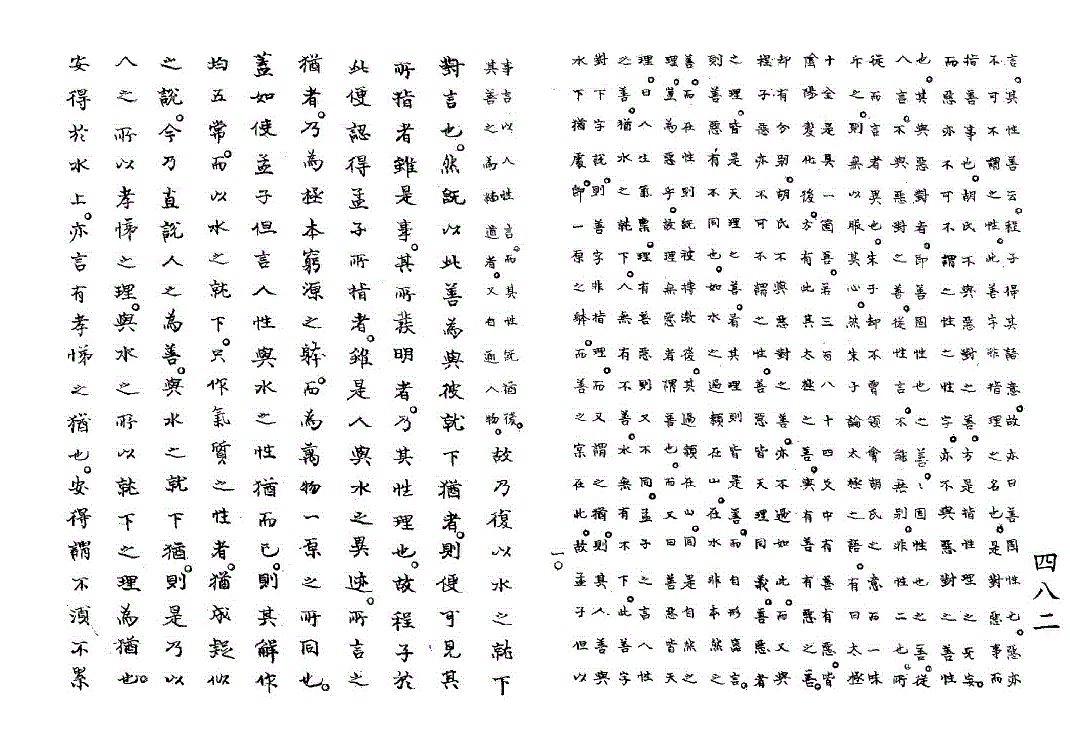 言。其性善云。程子得其语意。故亦曰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此善字非指理之名也。是对恶事而指善事也。胡氏不与恶对之善。方是指性理之无妄。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性字。亦不与恶对之善性也。其与恶对者。即善固性也之善。善固性也之善。从人言。不与恶对之善。从性言。不能无别。非性二也。所从而言者异也。朱子却不曾领会胡氏之意而一味斥之。则无以服其心。然朱子论太极之语。有曰太极十全是具一个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恶。皆阴阳变化后。方有此其太极之善。与有善有恶之善。却有分别。胡氏不与恶对之善。亦不过如此。而又与程子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同义。善恶者之理。皆是天理之善。看其理则皆是善。而自形器言。则善恶有不同也。如水之过颡在山。在水非本然之善。而在性则既被搏激后。其过颡在山。同是自然之理。岂为恶乎。故理无恶者谓善也。而又曰善恶皆天理。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则又不同。孟子之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此善字对下字说。则善字非指理。而又谓之犹。则其人善与水下犹处。即一原之体。而善之宲在此。故孟子但以事言以人性言。而其性既犹后。其善之为继道者。又自通人物。)故乃复以水之就下对言也。然既以此善为与彼就下犹者。则便可见其所指者虽是事。其所发明者。乃其性理也。故程子于此便认得孟子所指者。虽是人与水之异迹。所言之犹者。乃为极本穷源之体。而为万物一原之所同也。盖如使孟子但言人性与水之性犹而已。则其解作均五常。而以水之就下。只作气质之性者。犹成疑似之说。今乃直说人之为善。与水之就下犹。则是乃以人之所以孝悌之理。与水之所以就下之理为犹也。安得于水上。亦言有孝悌之犹也。安得谓不须不累
言。其性善云。程子得其语意。故亦曰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此善字非指理之名也。是对恶事而指善事也。胡氏不与恶对之善。方是指性理之无妄。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性字。亦不与恶对之善性也。其与恶对者。即善固性也之善。善固性也之善。从人言。不与恶对之善。从性言。不能无别。非性二也。所从而言者异也。朱子却不曾领会胡氏之意而一味斥之。则无以服其心。然朱子论太极之语。有曰太极十全是具一个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恶。皆阴阳变化后。方有此其太极之善。与有善有恶之善。却有分别。胡氏不与恶对之善。亦不过如此。而又与程子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同义。善恶者之理。皆是天理之善。看其理则皆是善。而自形器言。则善恶有不同也。如水之过颡在山。在水非本然之善。而在性则既被搏激后。其过颡在山。同是自然之理。岂为恶乎。故理无恶者谓善也。而又曰善恶皆天理。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则又不同。孟子之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此善字对下字说。则善字非指理。而又谓之犹。则其人善与水下犹处。即一原之体。而善之宲在此。故孟子但以事言以人性言。而其性既犹后。其善之为继道者。又自通人物。)故乃复以水之就下对言也。然既以此善为与彼就下犹者。则便可见其所指者虽是事。其所发明者。乃其性理也。故程子于此便认得孟子所指者。虽是人与水之异迹。所言之犹者。乃为极本穷源之体。而为万物一原之所同也。盖如使孟子但言人性与水之性犹而已。则其解作均五常。而以水之就下。只作气质之性者。犹成疑似之说。今乃直说人之为善。与水之就下犹。则是乃以人之所以孝悌之理。与水之所以就下之理为犹也。安得于水上。亦言有孝悌之犹也。安得谓不须不累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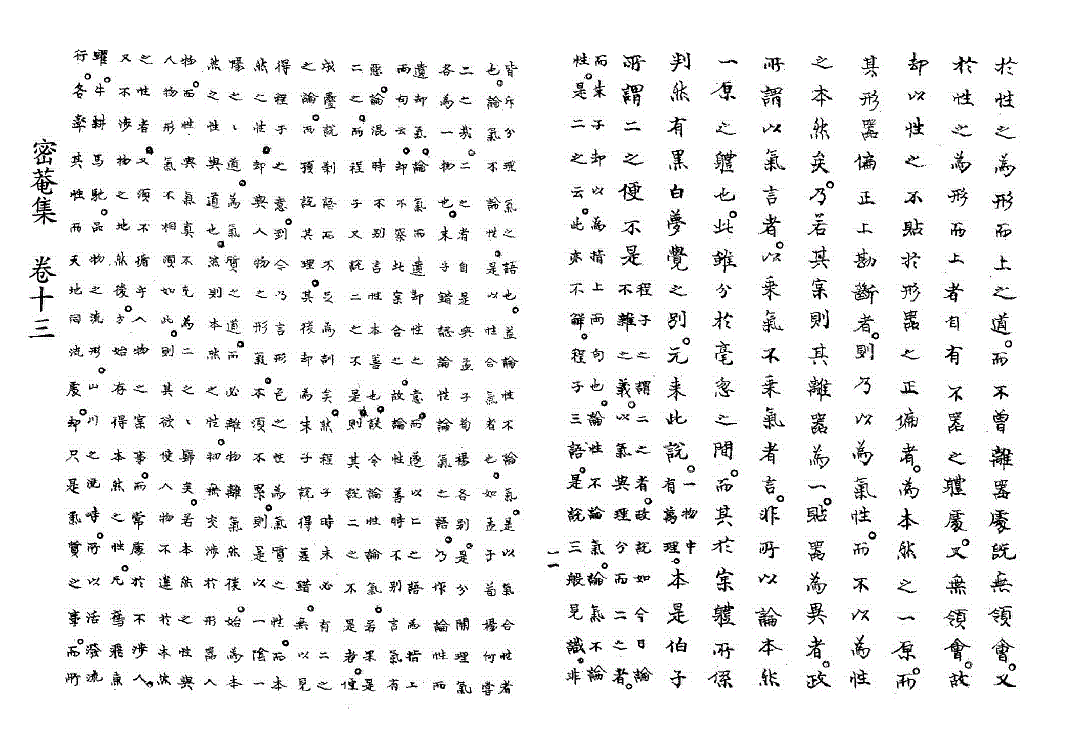 于性之为形而上之道。而不曾离器处既无领会。又于性之为形而上者自有不器之体处。又无领会。故却以性之不贴于形器之正偏者。为本然之一原。而其形器偏正上勘断者。则乃以为气性。而不以为性之本然矣。乃若其宲则其离器为一。贴器为异者。政所谓以气言者。以乘气不乘气者言。非所以论本然一原之体也。此虽分于毫忽之间。而其于宲体所系判然有黑白梦觉之别。元来此说。(一物中有万理。)本是伯子所谓二之便不是(程子之谓二之者。政说如今日论不杂之义。以气与理分而二之者。而朱子却以为指上两句也。论性不论气。论气不论性。是二之云。此亦不解。程子三语。是说三般见识。非皆斥分理气之语也。盖论性不论气。是以气合性者也。论气不论性。是以性合气者也。如孟子荀杨何尝二之哉。二之者自是与孟子荀杨各别。是分开理气各为一物也。朱子错认论性论气之语。乃作论性而遗却气。论气而遗却性之意。而遂以二之语为指上两句云。却不察此宲合之。故论性善时不别言气有恶。论混时不别言性本善也。设令论性论气。若果是二之。而程子又说二之不是。则其说二之不是者。便成叠说剩语而不足为训矣。然程子时未必有二之之论。而预说其理。其后却为朱子说得差错。无以见得程子之意。到今乃言形色之性为气质之性。而本然之性。却与人物之形气。不须不累。则是以一阴一阳之之道。为气质之道。而必离物离气然后。始为本然之性与道也。然则本然之性。初无交涉于形器人物。而性与气真不免为二之之归矣。若本然之性与人物形气不相须如此。则其欲使人物不违于本然之性者。又须不循乎人物之宲事。而常处于不涉人。又不涉物之地然后。方始存得本然之性。凡鸢飞鱼跃。牛耕马驰。品物之流形。山川之流峙。所以活泼流行。各率其性而天地同流处。却只是气质之事。而所)
于性之为形而上之道。而不曾离器处既无领会。又于性之为形而上者自有不器之体处。又无领会。故却以性之不贴于形器之正偏者。为本然之一原。而其形器偏正上勘断者。则乃以为气性。而不以为性之本然矣。乃若其宲则其离器为一。贴器为异者。政所谓以气言者。以乘气不乘气者言。非所以论本然一原之体也。此虽分于毫忽之间。而其于宲体所系判然有黑白梦觉之别。元来此说。(一物中有万理。)本是伯子所谓二之便不是(程子之谓二之者。政说如今日论不杂之义。以气与理分而二之者。而朱子却以为指上两句也。论性不论气。论气不论性。是二之云。此亦不解。程子三语。是说三般见识。非皆斥分理气之语也。盖论性不论气。是以气合性者也。论气不论性。是以性合气者也。如孟子荀杨何尝二之哉。二之者自是与孟子荀杨各别。是分开理气各为一物也。朱子错认论性论气之语。乃作论性而遗却气。论气而遗却性之意。而遂以二之语为指上两句云。却不察此宲合之。故论性善时不别言气有恶。论混时不别言性本善也。设令论性论气。若果是二之。而程子又说二之不是。则其说二之不是者。便成叠说剩语而不足为训矣。然程子时未必有二之之论。而预说其理。其后却为朱子说得差错。无以见得程子之意。到今乃言形色之性为气质之性。而本然之性。却与人物之形气。不须不累。则是以一阴一阳之之道。为气质之道。而必离物离气然后。始为本然之性与道也。然则本然之性。初无交涉于形器人物。而性与气真不免为二之之归矣。若本然之性与人物形气不相须如此。则其欲使人物不违于本然之性者。又须不循乎人物之宲事。而常处于不涉人。又不涉物之地然后。方始存得本然之性。凡鸢飞鱼跃。牛耕马驰。品物之流形。山川之流峙。所以活泼流行。各率其性而天地同流处。却只是气质之事。而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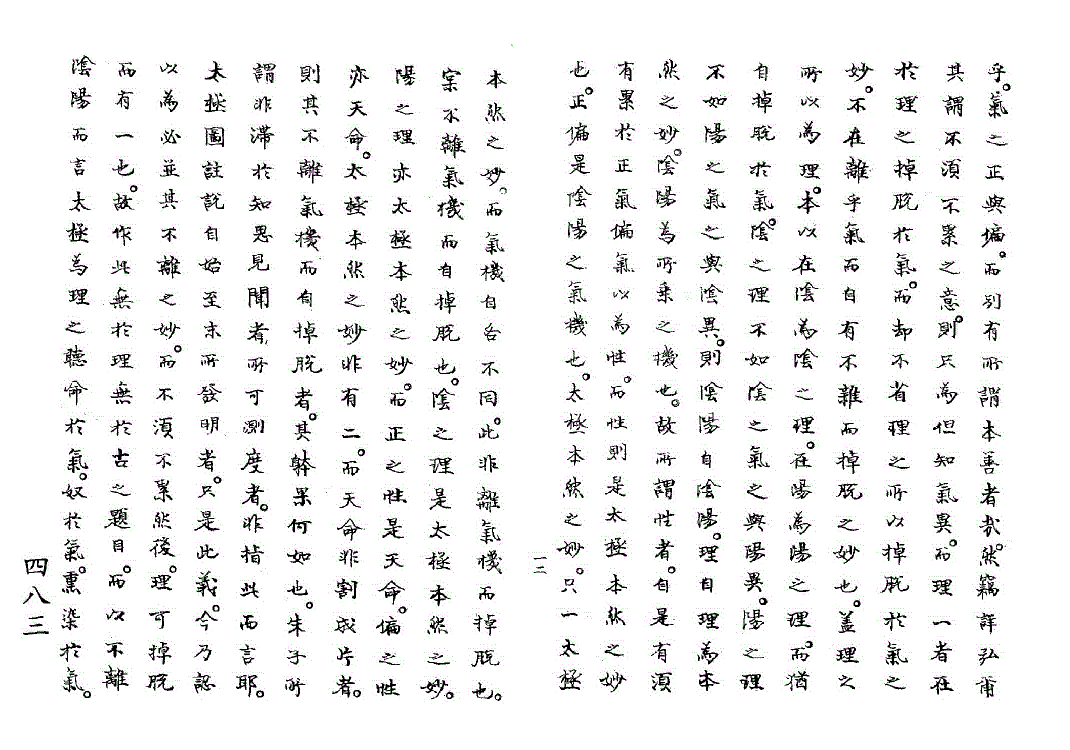 乎。气之正与偏。而别有所谓本善者哉。然窃详弘尔(一作甫)其谓不须不累之意。则只为但知气异。而理一者在于理之掉脱于气。而却不省理之所以掉脱于气之妙。不在离乎气而自有不杂而掉脱之妙也。盖理之所以为理。本以在阴为阴之理。在阳为阳之理。而犹自掉脱于气。阴之理不如阴之气之与阳异。阳之理不如阳之气之与阴异。则阴阳自阴阳。理自理为本然之妙。阴阳为所乘之机也。故所谓性者。自是有须有累于正气偏气以为性。而性则是太极本然之妙也。正偏是阴阳之气机也。太极本然之妙。只一太极本然之妙。而气机自各不同。此非离气机而掉脱也。宲不离气机而自掉脱也。阴之理是太极本然之妙。阳之理亦太极本然之妙。而正之性是天命。偏之性亦天命。太极本然之妙非有二。而天命非割成片者。则其不离气机而自掉脱者。其体果何如也。朱子所谓非滞于知思见闻者所可测度者。非指此而言耶。太极图注说自始至末所发明者。只是此义。今乃认以为必并其不离之妙。而不须不累然后。理可掉脱而有一也。故作此无于理无于古之题目。而以不离阴阳而言太极为理之听命于气。奴于气。熏染于气。
乎。气之正与偏。而别有所谓本善者哉。然窃详弘尔(一作甫)其谓不须不累之意。则只为但知气异。而理一者在于理之掉脱于气。而却不省理之所以掉脱于气之妙。不在离乎气而自有不杂而掉脱之妙也。盖理之所以为理。本以在阴为阴之理。在阳为阳之理。而犹自掉脱于气。阴之理不如阴之气之与阳异。阳之理不如阳之气之与阴异。则阴阳自阴阳。理自理为本然之妙。阴阳为所乘之机也。故所谓性者。自是有须有累于正气偏气以为性。而性则是太极本然之妙也。正偏是阴阳之气机也。太极本然之妙。只一太极本然之妙。而气机自各不同。此非离气机而掉脱也。宲不离气机而自掉脱也。阴之理是太极本然之妙。阳之理亦太极本然之妙。而正之性是天命。偏之性亦天命。太极本然之妙非有二。而天命非割成片者。则其不离气机而自掉脱者。其体果何如也。朱子所谓非滞于知思见闻者所可测度者。非指此而言耶。太极图注说自始至末所发明者。只是此义。今乃认以为必并其不离之妙。而不须不累然后。理可掉脱而有一也。故作此无于理无于古之题目。而以不离阴阳而言太极为理之听命于气。奴于气。熏染于气。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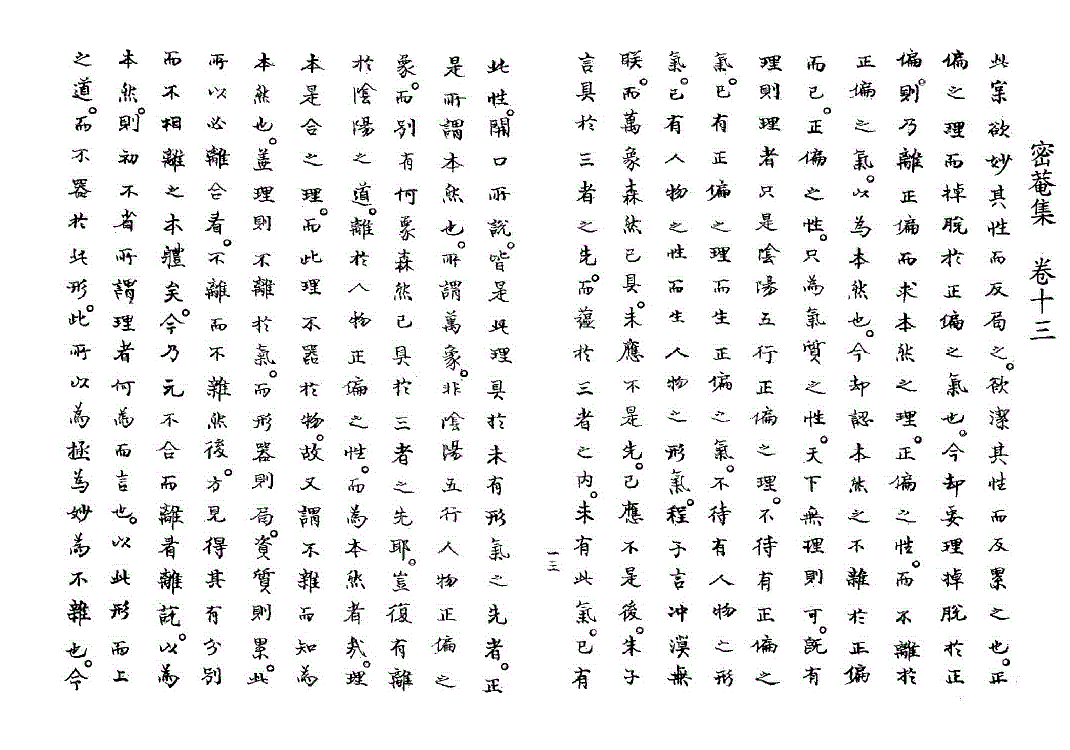 此宲欲妙其性而反局之。欲洁其性而反累之也。正偏之理而掉脱于正偏之气也。今却要理掉脱于正偏。则乃离正偏而求本然之理。正偏之性。而不离于正偏之气。以为本然也。今却认本然之不杂于正偏而已。正偏之性。只为气质之性。天下无理则可。既有理则理者只是阴阳五行正偏之理。不待有正偏之气。已有正偏之理而生正偏之气。不待有人物之形气。已有人物之性而生人物之形气。程子言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朱子言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未有此气。已有此性。开口所说。皆是此理具于未有形气之先者。正是所谓本然也。所谓万象。非阴阳五行人物正偏之象。而别有何象森然已具于三者之先耶。岂复有离于阴阳之道。离于人物正偏之性。而为本然者哉。理本是合之理。而此理不器于物。故又谓不杂而知为本然也。盖理则不离于气。而形器则局。资质则累。此所以必离合看。不离而不杂然后。方见得其有分别而不相离之本体矣。今乃元不合而离看离说。以为本然。则初不省所谓理者何为而言也。以此形而上之道。而不器于此形。此所以为极为妙为不杂也。今
此宲欲妙其性而反局之。欲洁其性而反累之也。正偏之理而掉脱于正偏之气也。今却要理掉脱于正偏。则乃离正偏而求本然之理。正偏之性。而不离于正偏之气。以为本然也。今却认本然之不杂于正偏而已。正偏之性。只为气质之性。天下无理则可。既有理则理者只是阴阳五行正偏之理。不待有正偏之气。已有正偏之理而生正偏之气。不待有人物之形气。已有人物之性而生人物之形气。程子言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朱子言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未有此气。已有此性。开口所说。皆是此理具于未有形气之先者。正是所谓本然也。所谓万象。非阴阳五行人物正偏之象。而别有何象森然已具于三者之先耶。岂复有离于阴阳之道。离于人物正偏之性。而为本然者哉。理本是合之理。而此理不器于物。故又谓不杂而知为本然也。盖理则不离于气。而形器则局。资质则累。此所以必离合看。不离而不杂然后。方见得其有分别而不相离之本体矣。今乃元不合而离看离说。以为本然。则初不省所谓理者何为而言也。以此形而上之道。而不器于此形。此所以为极为妙为不杂也。今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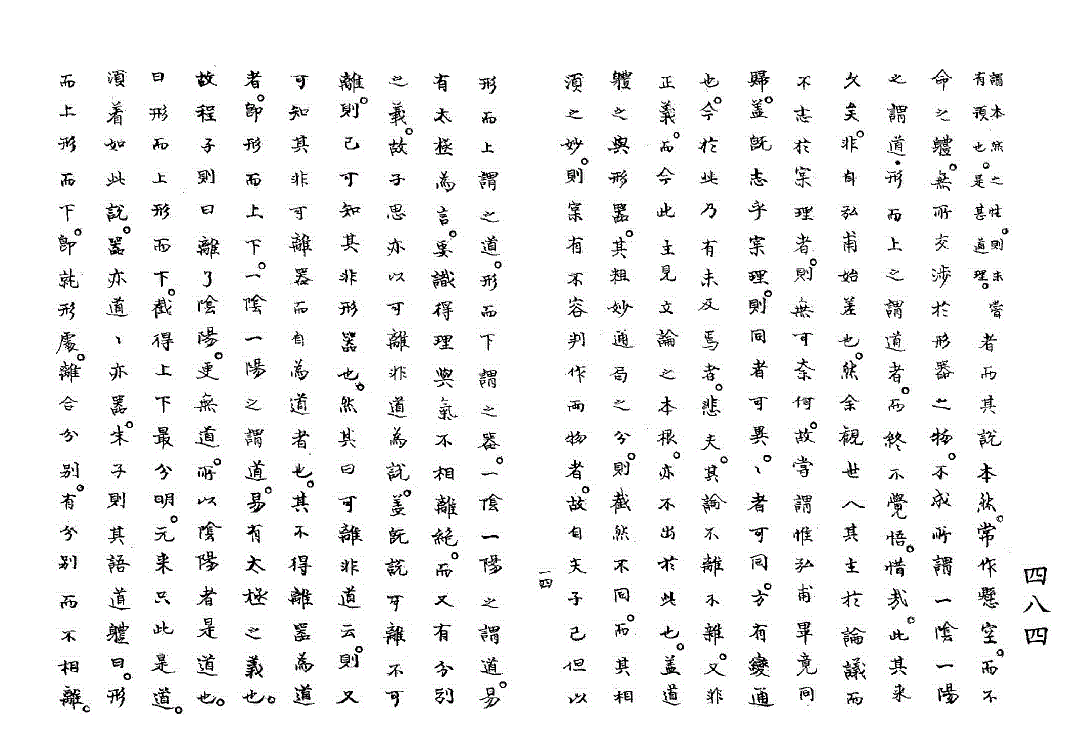 (谓本然之性。则未尝有预也。是甚道理。)者而其说本然。常作悬空。而不命之体。无所交涉于形器之物。不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之谓道者。而终不觉悟。惜哉。此其来久矣。非自弘甫始差也。然余观世人其主于论议而不志于宲理者。则无可奈何。故尝谓惟弘甫毕竟同归。盖既志乎宲理。则同者可异。异者可同。方有变通也。今于此乃有未及焉者。悲夫。其论不离不杂。又非正义。而今此主见立论之本根。亦不出于此也。盖道体之与形器。其粗妙通局之分。则截然不同。而其相须之妙。则宲有不容判作两物者。故自夫子已但以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为言。要识得理与气不相离绝。而又有分别之义。故子思亦以可离非道为说。盖既说可离不可离。则已可知其非形器也。然其曰可离非道云。则又可知其非可离器而自为道者也。其不得离器为道者。即形而上下。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之义也。故程子则曰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曰形而上形而下。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朱子则其语道体曰。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有分别而不相离。
(谓本然之性。则未尝有预也。是甚道理。)者而其说本然。常作悬空。而不命之体。无所交涉于形器之物。不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之谓道者。而终不觉悟。惜哉。此其来久矣。非自弘甫始差也。然余观世人其主于论议而不志于宲理者。则无可奈何。故尝谓惟弘甫毕竟同归。盖既志乎宲理。则同者可异。异者可同。方有变通也。今于此乃有未及焉者。悲夫。其论不离不杂。又非正义。而今此主见立论之本根。亦不出于此也。盖道体之与形器。其粗妙通局之分。则截然不同。而其相须之妙。则宲有不容判作两物者。故自夫子已但以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为言。要识得理与气不相离绝。而又有分别之义。故子思亦以可离非道为说。盖既说可离不可离。则已可知其非形器也。然其曰可离非道云。则又可知其非可离器而自为道者也。其不得离器为道者。即形而上下。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之义也。故程子则曰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曰形而上形而下。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朱子则其语道体曰。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有分别而不相离。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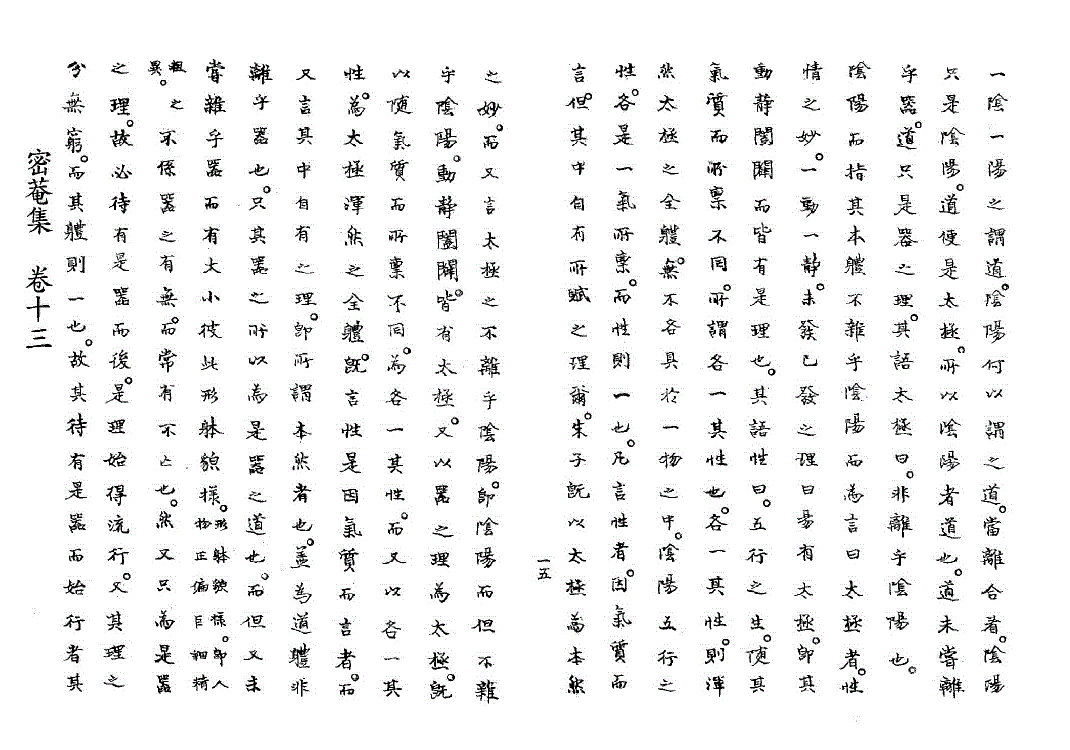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何以谓之道。当离合看。阴阳只是阴阳。道便是太极。所以阴阳者道也。道未尝离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其语太极曰。非离乎阴阳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何以谓之道。当离合看。阴阳只是阴阳。道便是太极。所以阴阳者道也。道未尝离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其语太极曰。非离乎阴阳也。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曰太极者。性情之妙。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曰易有太极。即其动静阖辟而皆有是理也。其语性曰。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阴阳五行之性。各是一气所禀。而性则一也。凡言性者。因气质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赋之理尔。朱子既以太极为本然之妙。而又言太极之不离乎阴阳。即阴阳而但不杂乎阴阳。动静阖辟。皆有太极。又以器之理为太极。既以随气质而所禀不同。为各一其性。而又以各一其性。为太极浑然之全体。既言性是因气质而言者。而又言其中自有之理。即所谓本然者也。盖为道体非离乎器也。只其器之所以为是器之道也。而但又未尝杂乎器而有大小彼此形体貌㨾。(形体貌样。即人物正偏巨细精粗之异。)不系器之有无。而常有不亡也。然又只为是器之理。故必待有是器而后。是理始得流行。又其理之分无穷。而其体则一也。故其待有是器而始行者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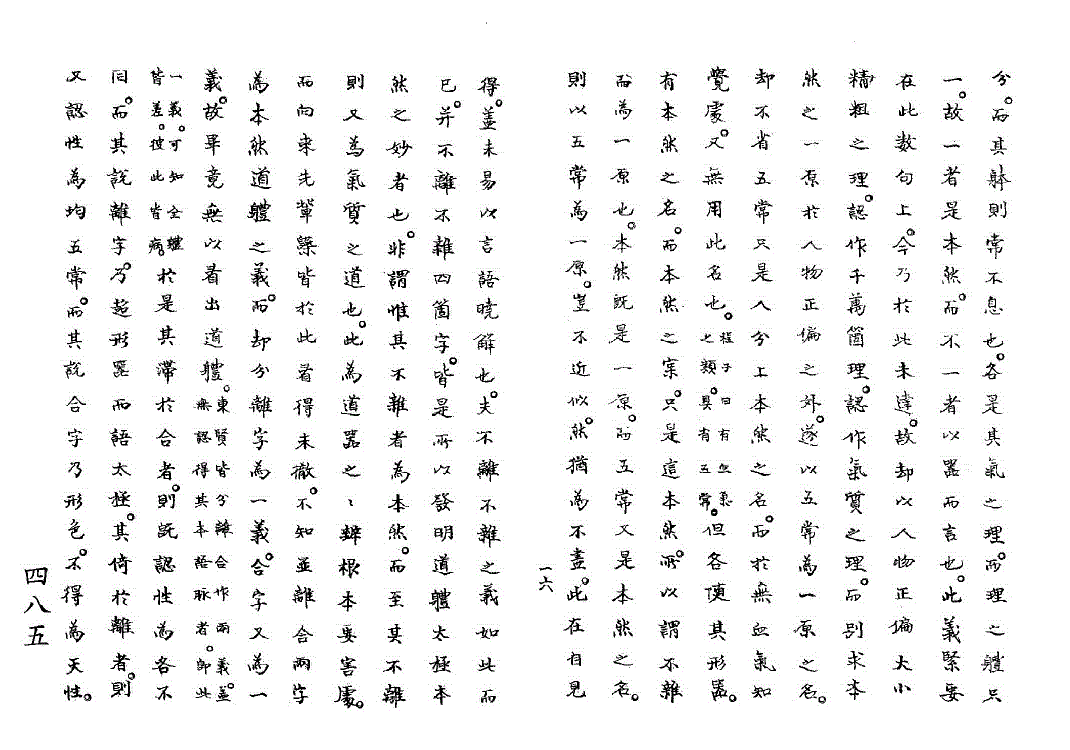 分。而其体则常不息也。各是其气之理。而理之体只一。故一者是本然。而不一者以器而言也。此义紧要在此数句上。今乃于此未达。故却以人物正偏大小精粗之理。认作千万个理。认作气质之理。而别求本然之一原于人物正偏之外。遂以五常为一原之名。却不省五常只是人分上本然之名。而于无血气知觉处。又无用此名也。(程子曰有血气之类。具有五常。)但各随其形器。有本然之名。而本然之宲。只是这本然。所以谓不杂而为一原也。本然既是一原。而五常又是本然之名。则以五常为一原。岂不近似。然犹为不尽。此在自见得。盖未易以言语晓解也。夫不离不杂之义如此而已。并不离不杂四个字。皆是所以发明道体太极本然之妙者也。非谓惟其不杂者为本然。而至其不离则又为气质之道也。此为道器之之辨根本要害处。而向来先辈槩皆于此看得未彻。不知并离合两字为本然道体之义。而却分离字为一义。合字又为一义。故毕竟无以看出道体。(东贤皆分离合作两义。盖无认得其本语脉者。即此一义。可知全体皆差。彼此皆病。)于是其滞于合者。则既认性为各不同。而其说离字。乃超形器而语太极。其倚于离者。则又认性为均五常。而其说合字乃形色。不得为天性。
分。而其体则常不息也。各是其气之理。而理之体只一。故一者是本然。而不一者以器而言也。此义紧要在此数句上。今乃于此未达。故却以人物正偏大小精粗之理。认作千万个理。认作气质之理。而别求本然之一原于人物正偏之外。遂以五常为一原之名。却不省五常只是人分上本然之名。而于无血气知觉处。又无用此名也。(程子曰有血气之类。具有五常。)但各随其形器。有本然之名。而本然之宲。只是这本然。所以谓不杂而为一原也。本然既是一原。而五常又是本然之名。则以五常为一原。岂不近似。然犹为不尽。此在自见得。盖未易以言语晓解也。夫不离不杂之义如此而已。并不离不杂四个字。皆是所以发明道体太极本然之妙者也。非谓惟其不杂者为本然。而至其不离则又为气质之道也。此为道器之之辨根本要害处。而向来先辈槩皆于此看得未彻。不知并离合两字为本然道体之义。而却分离字为一义。合字又为一义。故毕竟无以看出道体。(东贤皆分离合作两义。盖无认得其本语脉者。即此一义。可知全体皆差。彼此皆病。)于是其滞于合者。则既认性为各不同。而其说离字。乃超形器而语太极。其倚于离者。则又认性为均五常。而其说合字乃形色。不得为天性。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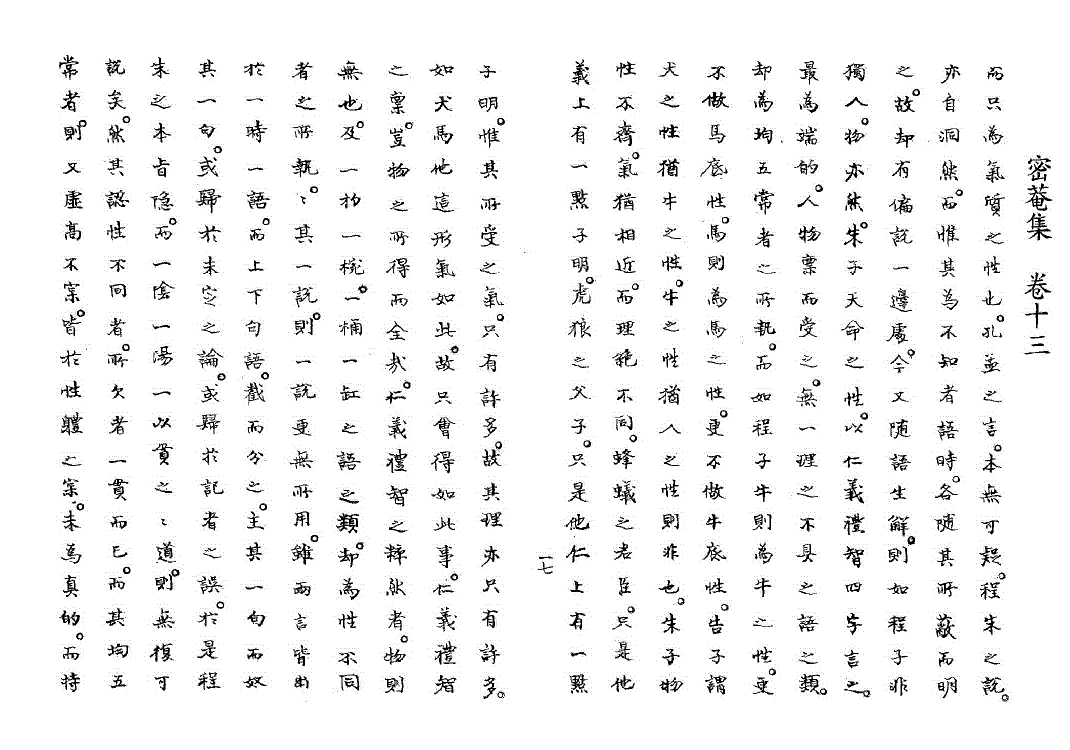 而只为气质之性也。孔孟之言。本无可疑。程朱之说。亦自洞然。而惟其为不知者语时。各随其所蔽而明之。故却有偏说一边处。今又随语生解。则如程子非独人。物亦然。朱子天命之性。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人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之语之类。却为均五常者之所执。而如程子牛则为牛之性。更不做马底性。马则为马之性。更不做牛底性。告子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则非也。朱子物性不齐。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惟其所受之气。只有许多。故其理亦只有许多。如犬马他这形气如此。故只会得如此事。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及一杓一碗。一桶一缸之语之类。却为性不同者之所执。执其一说。则一说更无所用。虽两言皆出于一时一语。而上下句语。截而分之。主其一句而奴其一句。或归于未定之论。或归于记者之误。于是程朱之本旨隐。而一阴一阳一以贯之之道。则无复可说矣。然其认性不同者。所欠者一贯而已。而其均五常者。则又虚高不宲。皆于性体之宲。未为真的。而持
而只为气质之性也。孔孟之言。本无可疑。程朱之说。亦自洞然。而惟其为不知者语时。各随其所蔽而明之。故却有偏说一边处。今又随语生解。则如程子非独人。物亦然。朱子天命之性。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人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之语之类。却为均五常者之所执。而如程子牛则为牛之性。更不做马底性。马则为马之性。更不做牛底性。告子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则非也。朱子物性不齐。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惟其所受之气。只有许多。故其理亦只有许多。如犬马他这形气如此。故只会得如此事。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及一杓一碗。一桶一缸之语之类。却为性不同者之所执。执其一说。则一说更无所用。虽两言皆出于一时一语。而上下句语。截而分之。主其一句而奴其一句。或归于未定之论。或归于记者之误。于是程朱之本旨隐。而一阴一阳一以贯之之道。则无复可说矣。然其认性不同者。所欠者一贯而已。而其均五常者。则又虚高不宲。皆于性体之宲。未为真的。而持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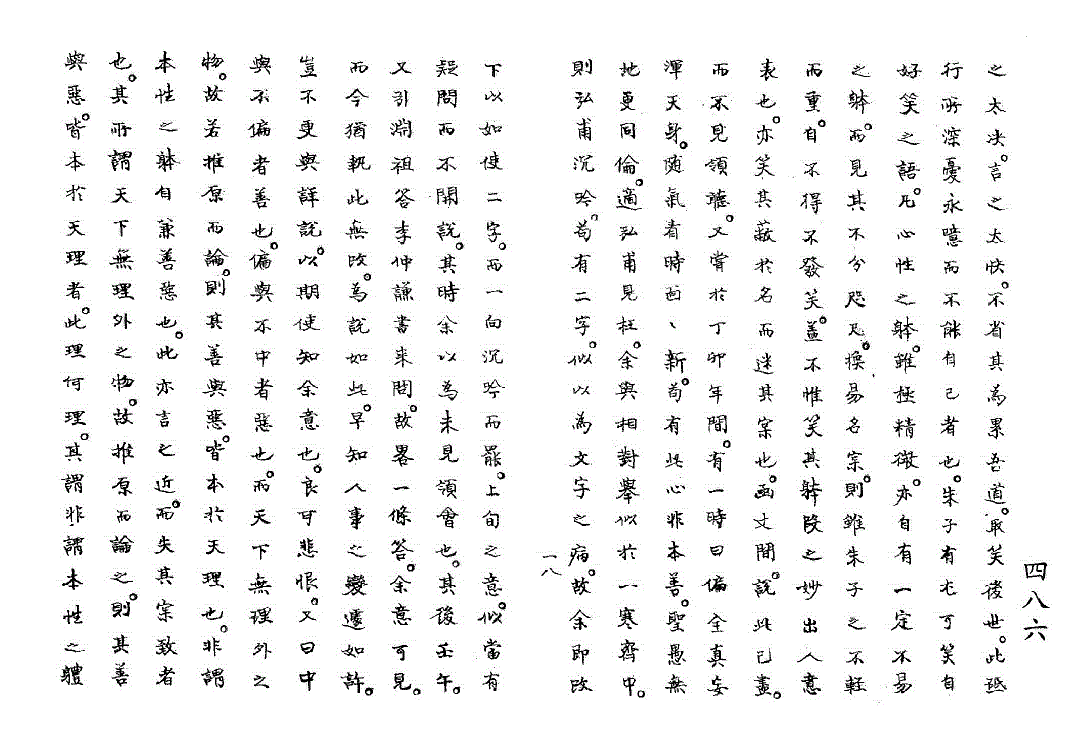 之太决。言之太快。不省其为累吾道。取笑后世。此砥行所深忧永噫而不能自已者也。朱子有尤可笑自好笑之语。凡心性之体。虽极精微。亦自有一定不易之体。而见其不分咫尺。换易名宲。则虽朱子之不轻而重。自不得不发笑。盖不惟笑其体段之妙出人意表也。亦笑其蔽于名而迷其宲也。函丈间。说此已尽。而不见领听。又尝于丁卯年间。有一时(一作诗)曰偏全真妄浑天身。随气看时面面新。苟有此心非本善。圣愚无地更同伦。适弘甫见枉。余与相对举似于一寒齐中。则弘甫沉吟。苟有二字。似以为文字之病。故余即改下以如使二字。而一向沉吟而罢。上旬(一作句)之意。似当有疑问而不开说。其时余以为未见领会也。其后壬午。又引渊祖答李仲谦书来问。故略一条答。余意可见。而今犹执此无改。为说如此。早知人事之变遽如许。岂不更与详说。以期使知余意也。良可悲恨。又曰中与不偏者善也。偏与不中者恶也。而天下无理外之物。故若推原而论。则其善与恶。皆本于天理也。非谓本性之体自兼善恶也。此亦言之近。而失其宲致者也。其所谓天下无理外之物。故推原而论之。则其善与恶。皆本于天理者。此理何理。其谓非谓本性之体
之太决。言之太快。不省其为累吾道。取笑后世。此砥行所深忧永噫而不能自已者也。朱子有尤可笑自好笑之语。凡心性之体。虽极精微。亦自有一定不易之体。而见其不分咫尺。换易名宲。则虽朱子之不轻而重。自不得不发笑。盖不惟笑其体段之妙出人意表也。亦笑其蔽于名而迷其宲也。函丈间。说此已尽。而不见领听。又尝于丁卯年间。有一时(一作诗)曰偏全真妄浑天身。随气看时面面新。苟有此心非本善。圣愚无地更同伦。适弘甫见枉。余与相对举似于一寒齐中。则弘甫沉吟。苟有二字。似以为文字之病。故余即改下以如使二字。而一向沉吟而罢。上旬(一作句)之意。似当有疑问而不开说。其时余以为未见领会也。其后壬午。又引渊祖答李仲谦书来问。故略一条答。余意可见。而今犹执此无改。为说如此。早知人事之变遽如许。岂不更与详说。以期使知余意也。良可悲恨。又曰中与不偏者善也。偏与不中者恶也。而天下无理外之物。故若推原而论。则其善与恶。皆本于天理也。非谓本性之体自兼善恶也。此亦言之近。而失其宲致者也。其所谓天下无理外之物。故推原而论之。则其善与恶。皆本于天理者。此理何理。其谓非谓本性之体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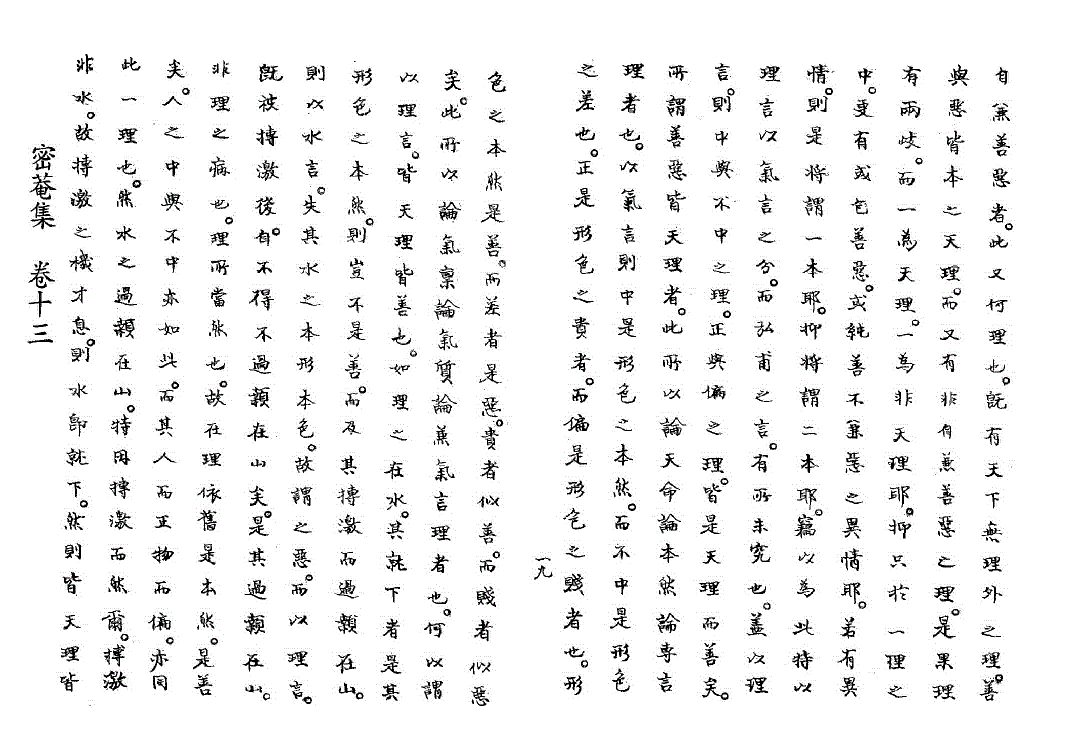 自兼善恶者。此又何理也。既有天下无理外之理。善与恶皆本之天理。而又有非自兼善恶之理。是果理有两歧。而一为天理。一为非天理耶。抑只于一理之中。更有或包善恶。或纯善不兼恶之异情耶。若有异情。则是将谓一本耶。抑将谓二本耶。窃以为此特以理言以气言之分。而弘甫之言。有所未究也。盖以理言。则中与不中之理。正与偏之理。皆是天理而善矣。所谓善恶皆天理者。此所以论天命论本然论专言理者也。以气言则中是形色之本然。而不中是形色之差也。正是形色之贵者。而偏是形色之贱者也。形色之本然是善。而差者是恶。贵者似善。而贱者似恶矣。此所以论气禀论气质论兼气言理者也。何以谓以理言。皆天理皆善也。如理之在水。其就下者是其形色之本然。则岂不是善。而及其搏激而过颡在山。则以水言。失其水之本形本色。故谓之恶。而以理言。既被搏激后。自不得不过颡在山矣。是其过颡在山。非理之病也。理所当然也。故在理依旧是本然。是善矣。人之中与不中亦如此。而其人而正物而偏。亦同此一理也。然水之过颡在山。特因搏激而然尔。搏激非水。故搏激之机才息。则水即就下。然则皆天理皆
自兼善恶者。此又何理也。既有天下无理外之理。善与恶皆本之天理。而又有非自兼善恶之理。是果理有两歧。而一为天理。一为非天理耶。抑只于一理之中。更有或包善恶。或纯善不兼恶之异情耶。若有异情。则是将谓一本耶。抑将谓二本耶。窃以为此特以理言以气言之分。而弘甫之言。有所未究也。盖以理言。则中与不中之理。正与偏之理。皆是天理而善矣。所谓善恶皆天理者。此所以论天命论本然论专言理者也。以气言则中是形色之本然。而不中是形色之差也。正是形色之贵者。而偏是形色之贱者也。形色之本然是善。而差者是恶。贵者似善。而贱者似恶矣。此所以论气禀论气质论兼气言理者也。何以谓以理言。皆天理皆善也。如理之在水。其就下者是其形色之本然。则岂不是善。而及其搏激而过颡在山。则以水言。失其水之本形本色。故谓之恶。而以理言。既被搏激后。自不得不过颡在山矣。是其过颡在山。非理之病也。理所当然也。故在理依旧是本然。是善矣。人之中与不中亦如此。而其人而正物而偏。亦同此一理也。然水之过颡在山。特因搏激而然尔。搏激非水。故搏激之机才息。则水即就下。然则皆天理皆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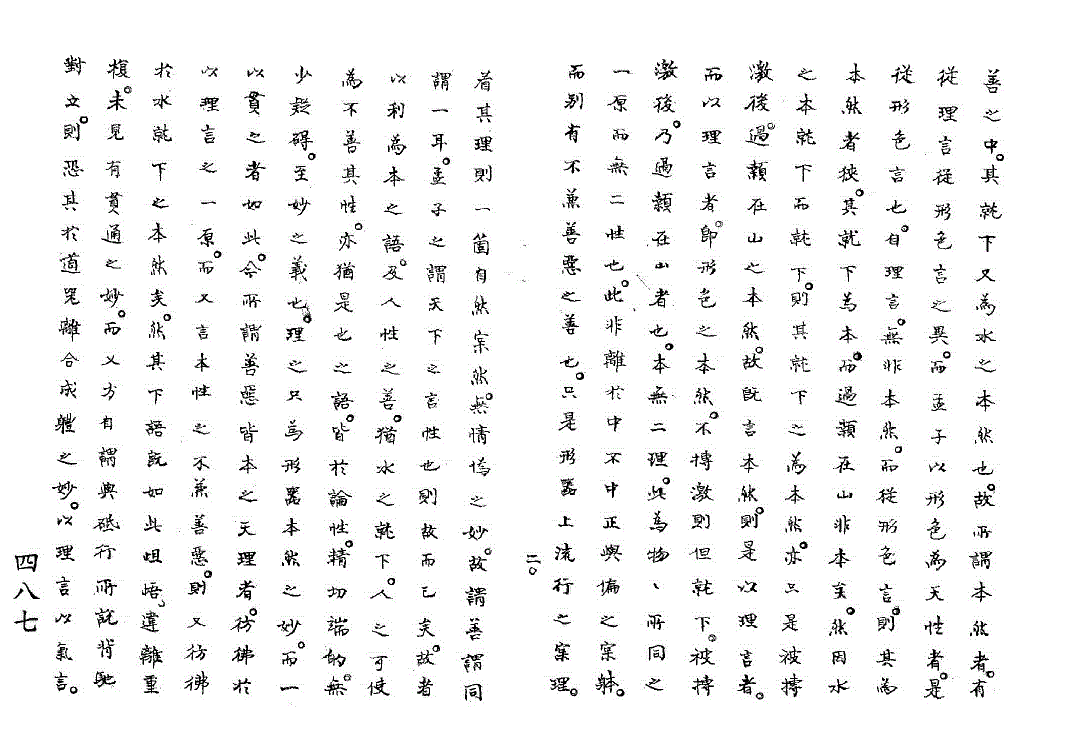 善之中。其就下又为水之本然也。故所谓本然者。有从理言从形色言之异。而孟子以形色为天性者。是从形色言也。自理言。无非本然。而从形色言。则其为本然者狭。其就下为本。而过颡在山非本矣。然因水之本就下而就下。则其就下之为本然。亦只是被搏激后。过颡在山之本然。故既言本然。则是以理言者。而以理言者。即形色之本然。不搏激则但就下。被搏激后。乃过颡在山者也。本无二理。此为物物所同之一原而无二性也。此非离于中不中正与偏之宲体。而别有不兼善恶之善也。只是形器上流行之宲理。看其理则一个自然宲然。无情伪之妙。故谓善谓同谓一耳。孟子之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之语。及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之语。皆于论性。精切端的。无少疑碍。至妙之义也。理之只为形器本然之妙。而一以贯之者如此。今所谓善恶皆本之天理者。彷佛于以理言之一原。而又言本性之不兼善恶。则又彷佛于水就下之本然矣。然其下语既如此龃龉。违离重复。未见有贯通之妙。而又方自谓与砥行所说背驰对立。则恐其于道器离合成体之妙。以理言以气言。
善之中。其就下又为水之本然也。故所谓本然者。有从理言从形色言之异。而孟子以形色为天性者。是从形色言也。自理言。无非本然。而从形色言。则其为本然者狭。其就下为本。而过颡在山非本矣。然因水之本就下而就下。则其就下之为本然。亦只是被搏激后。过颡在山之本然。故既言本然。则是以理言者。而以理言者。即形色之本然。不搏激则但就下。被搏激后。乃过颡在山者也。本无二理。此为物物所同之一原而无二性也。此非离于中不中正与偏之宲体。而别有不兼善恶之善也。只是形器上流行之宲理。看其理则一个自然宲然。无情伪之妙。故谓善谓同谓一耳。孟子之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之语。及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之语。皆于论性。精切端的。无少疑碍。至妙之义也。理之只为形器本然之妙。而一以贯之者如此。今所谓善恶皆本之天理者。彷佛于以理言之一原。而又言本性之不兼善恶。则又彷佛于水就下之本然矣。然其下语既如此龃龉。违离重复。未见有贯通之妙。而又方自谓与砥行所说背驰对立。则恐其于道器离合成体之妙。以理言以气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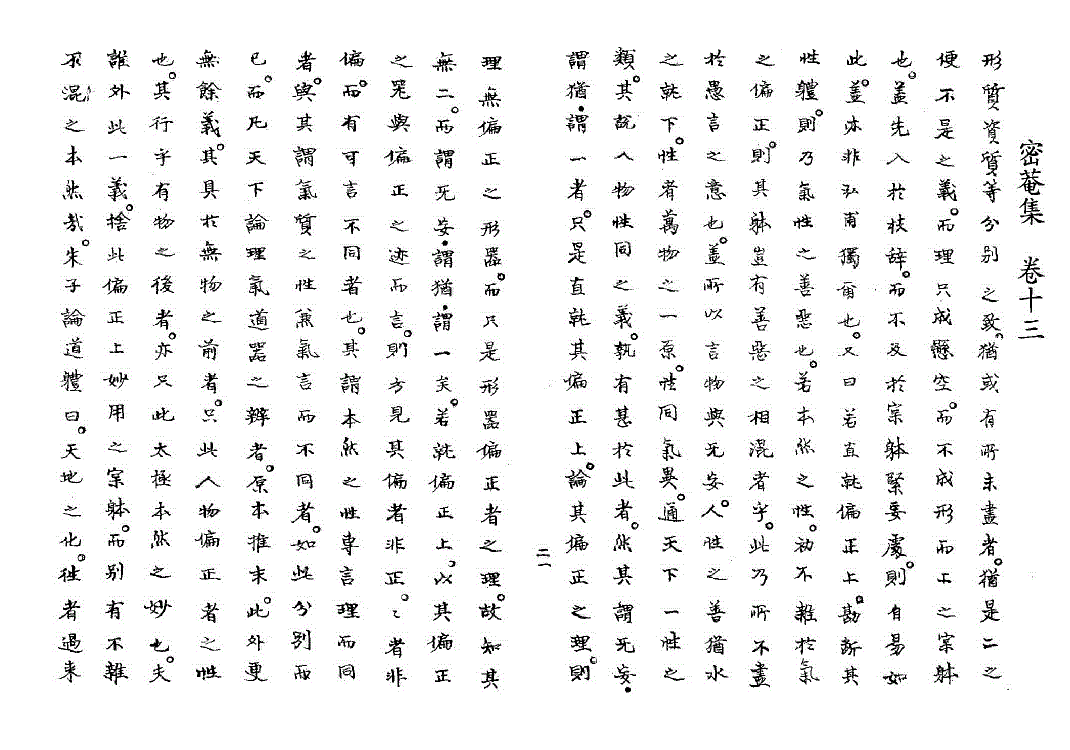 形质资质等分别之致。犹或有所未尽者。犹是二之便不是之义。而理只成悬空。而不成形而上之宲体也。盖先入于枝辞。而不及于宲体紧要处。则自易如此。盖亦非弘甫独尔也。又曰若直就偏正上。勘断其性体。则乃气性之善恶也。若本然之性。初不杂于气之偏正。则其体岂有善恶之相混者乎。此乃所不尽于愚言之意也。盖所以言物与无妄。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性者万物之一原。性同气异。通天下一性之类。其说人物性同之义。孰有甚于此者。然其谓无妄,谓犹,谓一者。只是直就其偏正上。论其偏正之理。则理无偏正之形器。而只是形器偏正者之理。故知其无二。而谓无妄,谓犹,谓一矣。若就偏正上。以其偏正之器与偏正之迹而言。则方见其偏者非正。正者非偏。而有可言不同者也。其谓本然之性专言理而同者。与其谓气质之性兼气言而不同者。如此分别而已。而凡天下论理气道器之辨者。原本推末。此外更无馀义。其具于无物之前者。只此人物偏正者之性也。其行乎有物之后者。亦只此太极本然之妙也。夫谁外此一义。舍此偏正上妙用之宲体。而别有不杂不混之本然哉。朱子论道体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
形质资质等分别之致。犹或有所未尽者。犹是二之便不是之义。而理只成悬空。而不成形而上之宲体也。盖先入于枝辞。而不及于宲体紧要处。则自易如此。盖亦非弘甫独尔也。又曰若直就偏正上。勘断其性体。则乃气性之善恶也。若本然之性。初不杂于气之偏正。则其体岂有善恶之相混者乎。此乃所不尽于愚言之意也。盖所以言物与无妄。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性者万物之一原。性同气异。通天下一性之类。其说人物性同之义。孰有甚于此者。然其谓无妄,谓犹,谓一者。只是直就其偏正上。论其偏正之理。则理无偏正之形器。而只是形器偏正者之理。故知其无二。而谓无妄,谓犹,谓一矣。若就偏正上。以其偏正之器与偏正之迹而言。则方见其偏者非正。正者非偏。而有可言不同者也。其谓本然之性专言理而同者。与其谓气质之性兼气言而不同者。如此分别而已。而凡天下论理气道器之辨者。原本推末。此外更无馀义。其具于无物之前者。只此人物偏正者之性也。其行乎有物之后者。亦只此太极本然之妙也。夫谁外此一义。舍此偏正上妙用之宲体。而别有不杂不混之本然哉。朱子论道体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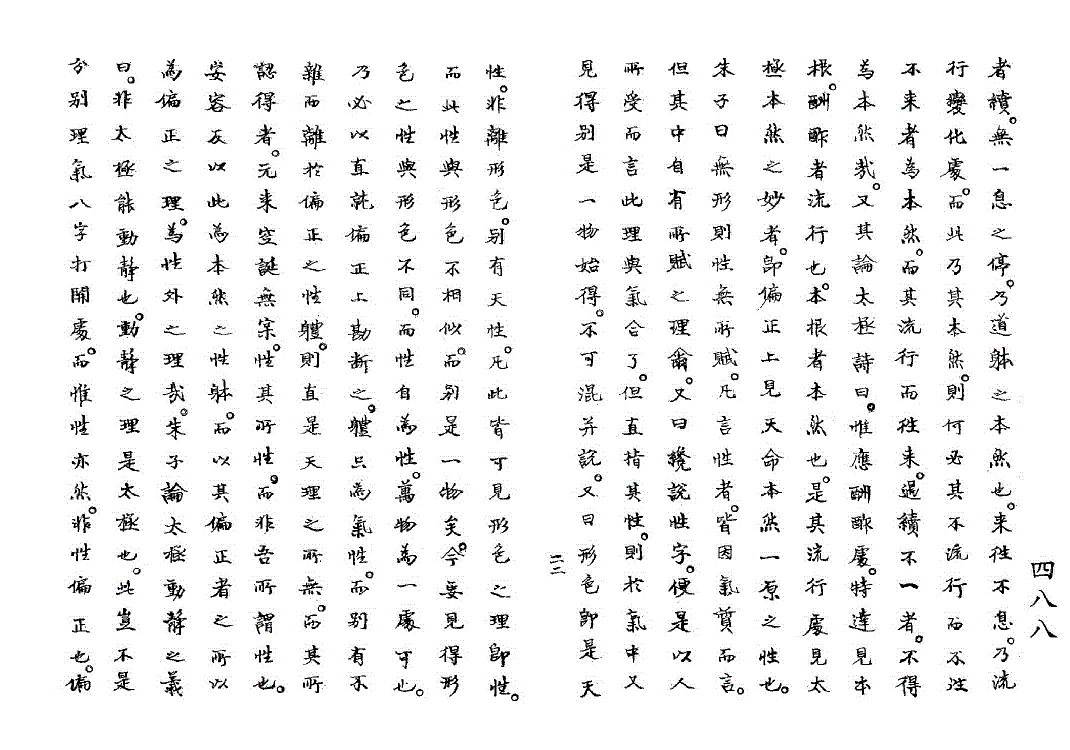 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来往不息。乃流行变化处。而此乃其本然。则何必其不流行而不往不来者为本然。而其流行而往来。过续不一者。不得为本然哉。又其论太极诗曰。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酬酢者流行也。本根者本然也。是其流行处见太极本然之妙者。即偏正上见天命本然一原之性也。朱子曰无形则性无所赋。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赋之理尔。又曰才说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与气合了。但直指其性。则于气中又见得别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说。又曰形色即是天性。非离形色。别有天性。凡此皆可见形色之理即性。而此性与形色不相似。而别是一物矣。今要见得形色之性与形色不同。而性自为性。万物为一处可也。乃必以直就偏正上勘断之。体只为气性。而别有不杂而离于偏正之性体。则直是天理之所无。而其所认得者。元来空诞无宲。性其所性。而非吾所谓性也。安容反以此为本然之性体。而以其偏正者之所以为偏正之理。为性外之理哉。朱子论太极动静之义曰。非太极能动静也。动静之理是太极也。此岂不是分别理气八字打开处。而惟性亦然。非性偏正也。偏
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来往不息。乃流行变化处。而此乃其本然。则何必其不流行而不往不来者为本然。而其流行而往来。过续不一者。不得为本然哉。又其论太极诗曰。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酬酢者流行也。本根者本然也。是其流行处见太极本然之妙者。即偏正上见天命本然一原之性也。朱子曰无形则性无所赋。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赋之理尔。又曰才说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与气合了。但直指其性。则于气中又见得别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说。又曰形色即是天性。非离形色。别有天性。凡此皆可见形色之理即性。而此性与形色不相似。而别是一物矣。今要见得形色之性与形色不同。而性自为性。万物为一处可也。乃必以直就偏正上勘断之。体只为气性。而别有不杂而离于偏正之性体。则直是天理之所无。而其所认得者。元来空诞无宲。性其所性。而非吾所谓性也。安容反以此为本然之性体。而以其偏正者之所以为偏正之理。为性外之理哉。朱子论太极动静之义曰。非太极能动静也。动静之理是太极也。此岂不是分别理气八字打开处。而惟性亦然。非性偏正也。偏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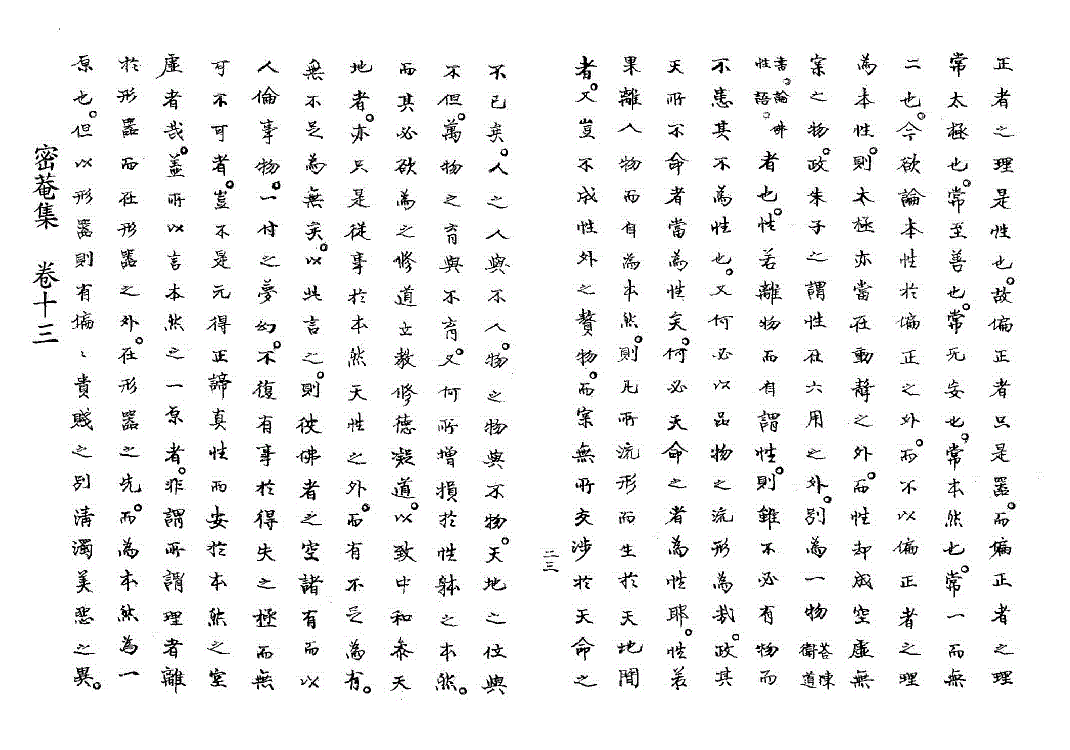 正者之理是性也。故偏正者只是器。而偏正者之理常太极也。常至善也。常无妄也。常本然也。常一而无二也。今欲论本性于偏正之外。而不以偏正者之理为本性。则太极亦当在动静之外。而性却成空虚无宲之物。政朱子之谓性在六用之外。别为一物(答陈卫道书。论佛性语。)者也。性若离物而自谓性。则虽不必有物而不患其不为性也。又何必以品物之流形为哉。政其天所不命者当为性矣。何必天命之者为性耶。性若果离人物而自为本然。则凡所流形而生于天地间者。又岂不成性外之赘物。而宲无所交涉于天命之不已矣。人之人与不人。物之物与不物。天地之位与不但(一作位)。万物之育与不育。又何所增损于性体之本然。而其必欲为之修道立教修德凝道。以致中和参天地者。亦只是从事于本然天性之外。而有不足为有。无不足为无矣。以此言之。则彼佛者之空诸有而以人伦事物。一付之梦幻。不复有事于得失之极而无可不可者。岂不是元得正谛真性而安于本然之空虚者哉。盖所以言本然之一原者。非谓所谓理者离于形器而在形器之外。在形器之先。而为本然为一原也。但以形器则有偏偏贵贱之别清浊美恶之异。
正者之理是性也。故偏正者只是器。而偏正者之理常太极也。常至善也。常无妄也。常本然也。常一而无二也。今欲论本性于偏正之外。而不以偏正者之理为本性。则太极亦当在动静之外。而性却成空虚无宲之物。政朱子之谓性在六用之外。别为一物(答陈卫道书。论佛性语。)者也。性若离物而自谓性。则虽不必有物而不患其不为性也。又何必以品物之流形为哉。政其天所不命者当为性矣。何必天命之者为性耶。性若果离人物而自为本然。则凡所流形而生于天地间者。又岂不成性外之赘物。而宲无所交涉于天命之不已矣。人之人与不人。物之物与不物。天地之位与不但(一作位)。万物之育与不育。又何所增损于性体之本然。而其必欲为之修道立教修德凝道。以致中和参天地者。亦只是从事于本然天性之外。而有不足为有。无不足为无矣。以此言之。则彼佛者之空诸有而以人伦事物。一付之梦幻。不复有事于得失之极而无可不可者。岂不是元得正谛真性而安于本然之空虚者哉。盖所以言本然之一原者。非谓所谓理者离于形器而在形器之外。在形器之先。而为本然为一原也。但以形器则有偏偏贵贱之别清浊美恶之异。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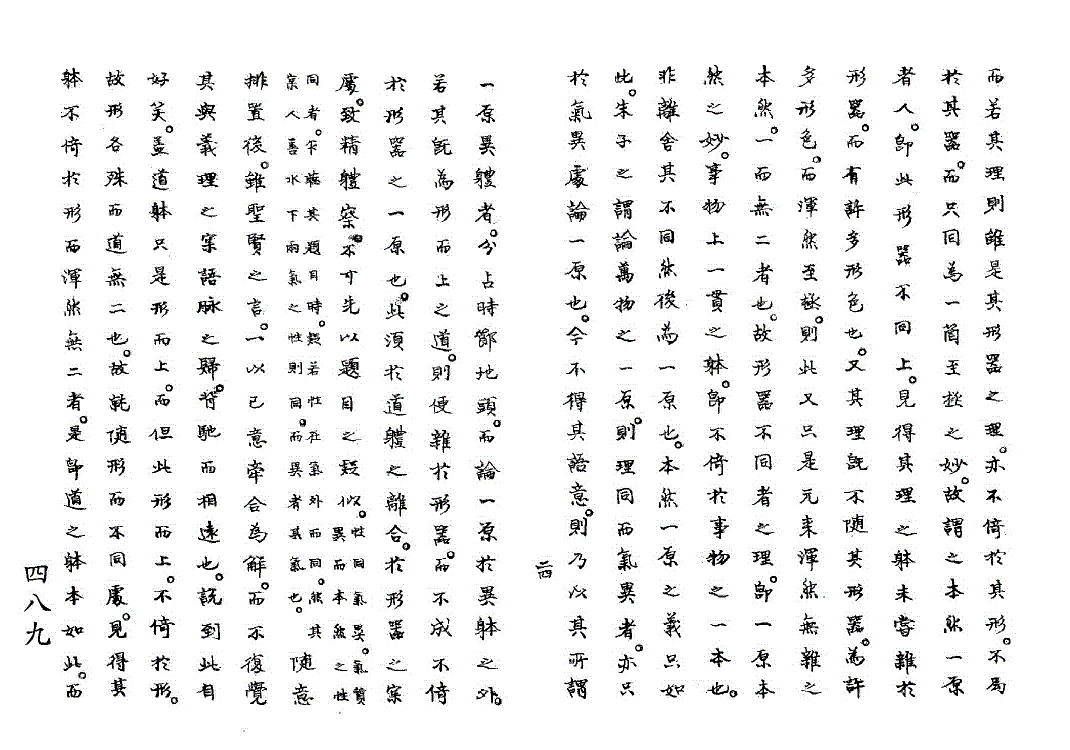 而若其理则虽是其形器之理。亦不倚于其形。不局于其器。而只同为一个至极之妙。故谓之本然一原者人。即此形器不同上。见得其理之体未尝杂于形器。而有许多形色也。又其理既不随其形器。为许多形色。而浑然至极。则此又只是元来浑然无杂之本然。一而无二者也。故形器不同者之理。即一原本然之妙。事物上一贯之体。即不倚于事物之一本也。非离舍其不同然后为一原也。本然一原之义只如此。朱子之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者。亦只于气异处论一原也。今不得其语意。则乃以其所谓一原异体者。分占时节地头。而论一原于异体之外。若其既为形而上之道。则便杂于形器。而不成不倚于形器之一原也。此须于道体之离合。于形器之宲处。致精体察。不可先以题目之疑似。(性同气异。气质异而本然之性同者。乍听其题目时。疑若性在气外而同。然其宲人善水下两气之性则同。而异者其气也。)随意排置后。虽圣贤之言。一以己意牵合为解。而不复觉其与义理之宲语脉之归。背驰而相远也。说到此自好笑。盖道体只是形而上。而但此形而上。不倚于形。故形各殊而道无二也。故就随形而不同处。见得其体不倚于形而浑然无二者。是即道之体本如此。而
而若其理则虽是其形器之理。亦不倚于其形。不局于其器。而只同为一个至极之妙。故谓之本然一原者人。即此形器不同上。见得其理之体未尝杂于形器。而有许多形色也。又其理既不随其形器。为许多形色。而浑然至极。则此又只是元来浑然无杂之本然。一而无二者也。故形器不同者之理。即一原本然之妙。事物上一贯之体。即不倚于事物之一本也。非离舍其不同然后为一原也。本然一原之义只如此。朱子之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者。亦只于气异处论一原也。今不得其语意。则乃以其所谓一原异体者。分占时节地头。而论一原于异体之外。若其既为形而上之道。则便杂于形器。而不成不倚于形器之一原也。此须于道体之离合。于形器之宲处。致精体察。不可先以题目之疑似。(性同气异。气质异而本然之性同者。乍听其题目时。疑若性在气外而同。然其宲人善水下两气之性则同。而异者其气也。)随意排置后。虽圣贤之言。一以己意牵合为解。而不复觉其与义理之宲语脉之归。背驰而相远也。说到此自好笑。盖道体只是形而上。而但此形而上。不倚于形。故形各殊而道无二也。故就随形而不同处。见得其体不倚于形而浑然无二者。是即道之体本如此。而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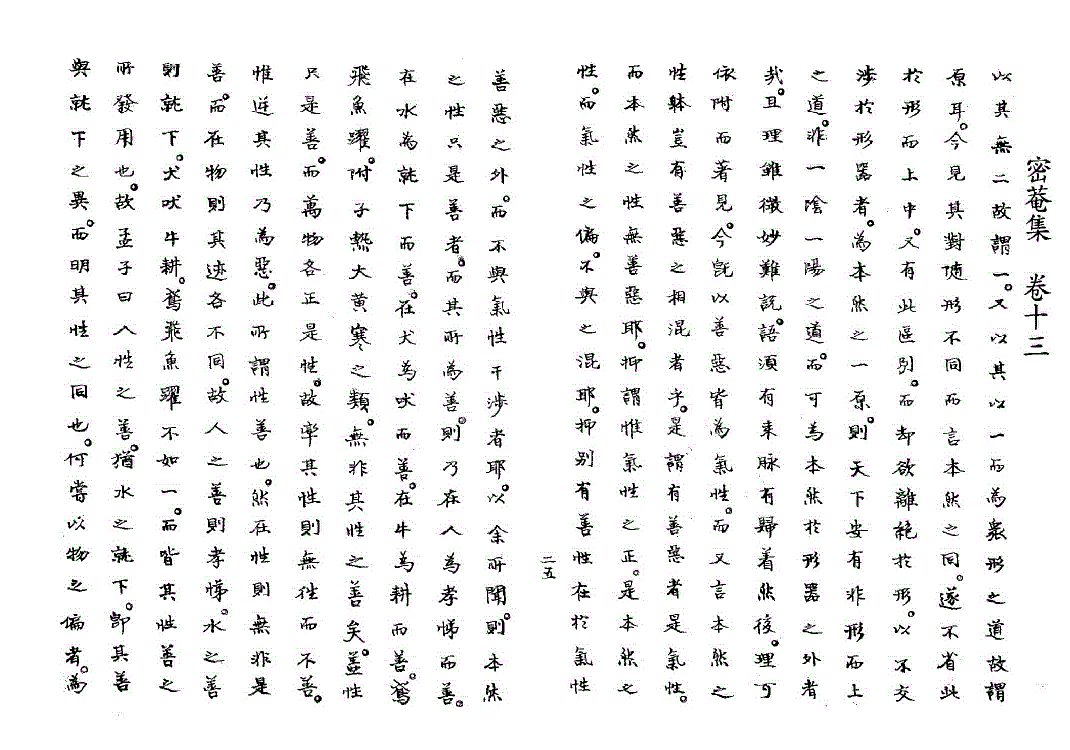 以其无二故谓一。又以其以一而为众形之道故谓原耳。今见其对随形不同而言本然之同。遂不省此于形而上中。又有此区别。而却欲离绝于形。以不交涉于形器者。为本然之一原。则天下安有非形而上之道。非一阴一阳之道。而可为本然于形器之外者哉。且理虽微妙难说。语须有来脉有归着然后。理可依附而著见。今既以善恶皆为气性。而又言本然之性体岂有善恶之相混者乎。是谓有善恶者是气性。而本然之性无善恶耶。抑谓惟气性之正。是本然之性。而气性之偏。不与之混耶。抑别有善性在于气性善恶之外。而不与气性干涉者耶。以余所闻。则本然之性只是善者。而其所为善。则乃在人为孝悌而善。在水为就下而善。在犬为吠而善。在牛为耕而善。鸢飞鱼跃。附子热大黄寒之类。无非其性之善矣。盖性只是善。而万物各正是性。故率其性则无往而不善。惟逆其性乃为恶。此所谓性善也。然在性则无非是善。而在物则其迹各不同。故人之善则孝悌。水之善则就下。犬吠牛耕。鸢飞鱼跃不如一。而皆其性善之所发用也。故孟子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即其善与就下之异。而明其性之同也。何尝以物之偏者。为
以其无二故谓一。又以其以一而为众形之道故谓原耳。今见其对随形不同而言本然之同。遂不省此于形而上中。又有此区别。而却欲离绝于形。以不交涉于形器者。为本然之一原。则天下安有非形而上之道。非一阴一阳之道。而可为本然于形器之外者哉。且理虽微妙难说。语须有来脉有归着然后。理可依附而著见。今既以善恶皆为气性。而又言本然之性体岂有善恶之相混者乎。是谓有善恶者是气性。而本然之性无善恶耶。抑谓惟气性之正。是本然之性。而气性之偏。不与之混耶。抑别有善性在于气性善恶之外。而不与气性干涉者耶。以余所闻。则本然之性只是善者。而其所为善。则乃在人为孝悌而善。在水为就下而善。在犬为吠而善。在牛为耕而善。鸢飞鱼跃。附子热大黄寒之类。无非其性之善矣。盖性只是善。而万物各正是性。故率其性则无往而不善。惟逆其性乃为恶。此所谓性善也。然在性则无非是善。而在物则其迹各不同。故人之善则孝悌。水之善则就下。犬吠牛耕。鸢飞鱼跃不如一。而皆其性善之所发用也。故孟子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即其善与就下之异。而明其性之同也。何尝以物之偏者。为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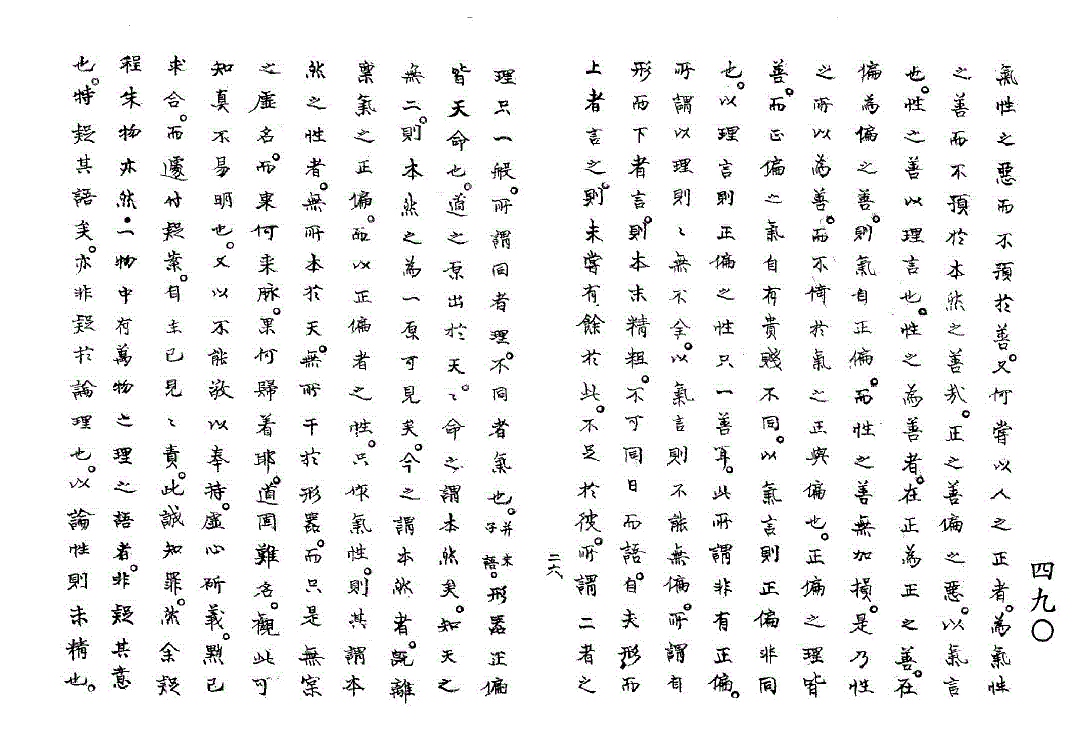 气性之恶而不预于善。又何尝以人之正者。为气性之善而不预于本然之善哉。正之善偏之恶。以气言也。性之善以理言也。性之为善者。在正为正之善。在偏为偏之善。则气自正偏。而性之善无加损。是乃性之所以为善。而不倚于气之正与偏也。正偏之理皆善。而正偏之气自有贵贱不同。以气言则正偏非同也。以理言则正偏之性只一善耳。此所谓非有正偏。所谓以理则则无不全。以气言则不能无偏。所谓自形而下者言。则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语。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则未尝有馀于此。不足于彼。所谓二者之理只一般。所谓同者理。不同者气也。(并朱子语。)形器正偏皆天命也。道之原出于天。天命之谓本然矣。知天之无二。则本然之为一原可见矣。今之谓本然者。既离禀气之正偏。而以正偏者之性。只作气性。则其谓本然之性者。无所本于天。无所干于形器。而只是无宲之虚名。而果何来脉。果何归着耶。道固难名。观此可知真不易明也。又以不能敬以奉持。虚心斫义。黜己求合。而遽付疑案。自主己见见责。此诚知罪。然余疑程朱物亦然,一物中有万物之理之语者。非疑其意也。特疑其语矣。亦非疑于论理也。以论性则未精也。
气性之恶而不预于善。又何尝以人之正者。为气性之善而不预于本然之善哉。正之善偏之恶。以气言也。性之善以理言也。性之为善者。在正为正之善。在偏为偏之善。则气自正偏。而性之善无加损。是乃性之所以为善。而不倚于气之正与偏也。正偏之理皆善。而正偏之气自有贵贱不同。以气言则正偏非同也。以理言则正偏之性只一善耳。此所谓非有正偏。所谓以理则则无不全。以气言则不能无偏。所谓自形而下者言。则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语。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则未尝有馀于此。不足于彼。所谓二者之理只一般。所谓同者理。不同者气也。(并朱子语。)形器正偏皆天命也。道之原出于天。天命之谓本然矣。知天之无二。则本然之为一原可见矣。今之谓本然者。既离禀气之正偏。而以正偏者之性。只作气性。则其谓本然之性者。无所本于天。无所干于形器。而只是无宲之虚名。而果何来脉。果何归着耶。道固难名。观此可知真不易明也。又以不能敬以奉持。虚心斫义。黜己求合。而遽付疑案。自主己见见责。此诚知罪。然余疑程朱物亦然,一物中有万物之理之语者。非疑其意也。特疑其语矣。亦非疑于论理也。以论性则未精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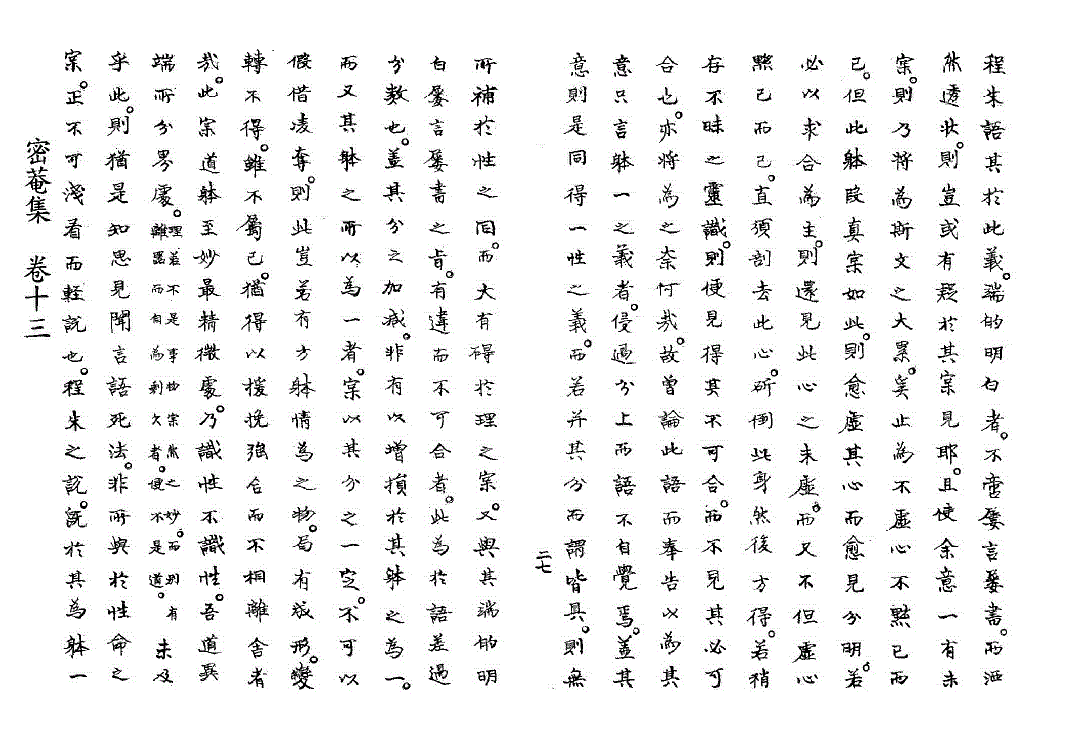 程朱语其于此义。端的明白者。不啻屡言屡书。而洒然透状。则岂或有疑于其宲见耶。且使余意一有未宲。则乃将为斯文之大累。奚止为不虚心不黜己而已。但此体段真宲如此。则愈虚其心而愈见分明。若必以求合为主。则还见此心之未虚。而又不但虚心黜己而已。直须剖去此心。斫倒此身然后方得。若稍存不昧之灵识。则便见得其不可合。而不见其必可合也。亦将为之奈何哉。故曾论此语而奉告以为其意只言体一之义者。侵过分上而语不自觉焉。盖其意则是同得一性之义。而若并其分而谓皆具。则无所补于性之同。而大有碍于理之宲。又与其端的明白屡言屡书之旨。有违而不可合者。此为于语差过分数也。盖其分之加减。非有以增损于其体之为一。而又其体之所以为一者。宲以其分之一定。不可以假借凌夺。则此岂若有方体情为之物。局有成形。变转不得。虽不属己。犹得以援挽强合而不相离舍者哉。此宲道体至妙最精微处。乃识性不识性。吾道异端所分界处。(理若不是事物宲然之妙。而别有离器而自为剩欠者。便不是道。)未及乎此。则犹是知思见闻言语死法。非所与于性命之宲。正不可浅看而轻说也。程朱之说。既于其为体一
程朱语其于此义。端的明白者。不啻屡言屡书。而洒然透状。则岂或有疑于其宲见耶。且使余意一有未宲。则乃将为斯文之大累。奚止为不虚心不黜己而已。但此体段真宲如此。则愈虚其心而愈见分明。若必以求合为主。则还见此心之未虚。而又不但虚心黜己而已。直须剖去此心。斫倒此身然后方得。若稍存不昧之灵识。则便见得其不可合。而不见其必可合也。亦将为之奈何哉。故曾论此语而奉告以为其意只言体一之义者。侵过分上而语不自觉焉。盖其意则是同得一性之义。而若并其分而谓皆具。则无所补于性之同。而大有碍于理之宲。又与其端的明白屡言屡书之旨。有违而不可合者。此为于语差过分数也。盖其分之加减。非有以增损于其体之为一。而又其体之所以为一者。宲以其分之一定。不可以假借凌夺。则此岂若有方体情为之物。局有成形。变转不得。虽不属己。犹得以援挽强合而不相离舍者哉。此宲道体至妙最精微处。乃识性不识性。吾道异端所分界处。(理若不是事物宲然之妙。而别有离器而自为剩欠者。便不是道。)未及乎此。则犹是知思见闻言语死法。非所与于性命之宲。正不可浅看而轻说也。程朱之说。既于其为体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1L 页
 处。发得无馀者。如其曰皆谓之性。则可于中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谓性循其性而不失者。是所谓道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更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更不做马底性。曰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曰天下雷行。付与无妄。天性岂有妄耶。圣人以茂树时育万物各使得其性也。曰洪纤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妄。(无有差妄者。洪则洪而不纤。纤则纤而不洪。高下亦然。万物亦然。此正解物与无妄之义。有父子则有慈孝之理。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与此一义。不容无父子而亦有慈孝之理。无耳目而亦有聪明之德。于父亦有孝理。于目亦有聪理。如此儱侗钝死。以为物与之无妄也。)物与无妄也。曰物理从来齐。物形从来不齐。曰此个义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见。(今谓人物性不同者。初不省此齐字。不在于不少不剩之外。固无可言。今谓人物均具五常之全者。又只知形而下之齐与不少不剩。必其件数不漏。方成其齐与不少不剩。而不省形而上之齐与不少不剩。却不系其件数之多少全不全。而随所在。只是这个。故无不齐而不少不剩也。须是于此着一眼目。曾子唯字。正此地位。程朱之后言一理者。卒未见一人端的到此。今之纷然。亦无足怪。)程子此诸语。说出无馀。皆与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形色天性等为一义。即其所循之异迹。而天命本然一而无二之意也。非牛有牛性而更有马底性。马有马性而更有牛底性。人有人性而更有物底性。物有物性而更有
处。发得无馀者。如其曰皆谓之性。则可于中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谓性循其性而不失者。是所谓道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更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更不做马底性。曰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曰天下雷行。付与无妄。天性岂有妄耶。圣人以茂树时育万物各使得其性也。曰洪纤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妄。(无有差妄者。洪则洪而不纤。纤则纤而不洪。高下亦然。万物亦然。此正解物与无妄之义。有父子则有慈孝之理。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与此一义。不容无父子而亦有慈孝之理。无耳目而亦有聪明之德。于父亦有孝理。于目亦有聪理。如此儱侗钝死。以为物与之无妄也。)物与无妄也。曰物理从来齐。物形从来不齐。曰此个义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见。(今谓人物性不同者。初不省此齐字。不在于不少不剩之外。固无可言。今谓人物均具五常之全者。又只知形而下之齐与不少不剩。必其件数不漏。方成其齐与不少不剩。而不省形而上之齐与不少不剩。却不系其件数之多少全不全。而随所在。只是这个。故无不齐而不少不剩也。须是于此着一眼目。曾子唯字。正此地位。程朱之后言一理者。卒未见一人端的到此。今之纷然。亦无足怪。)程子此诸语。说出无馀。皆与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形色天性等为一义。即其所循之异迹。而天命本然一而无二之意也。非牛有牛性而更有马底性。马有马性而更有牛底性。人有人性而更有物底性。物有物性而更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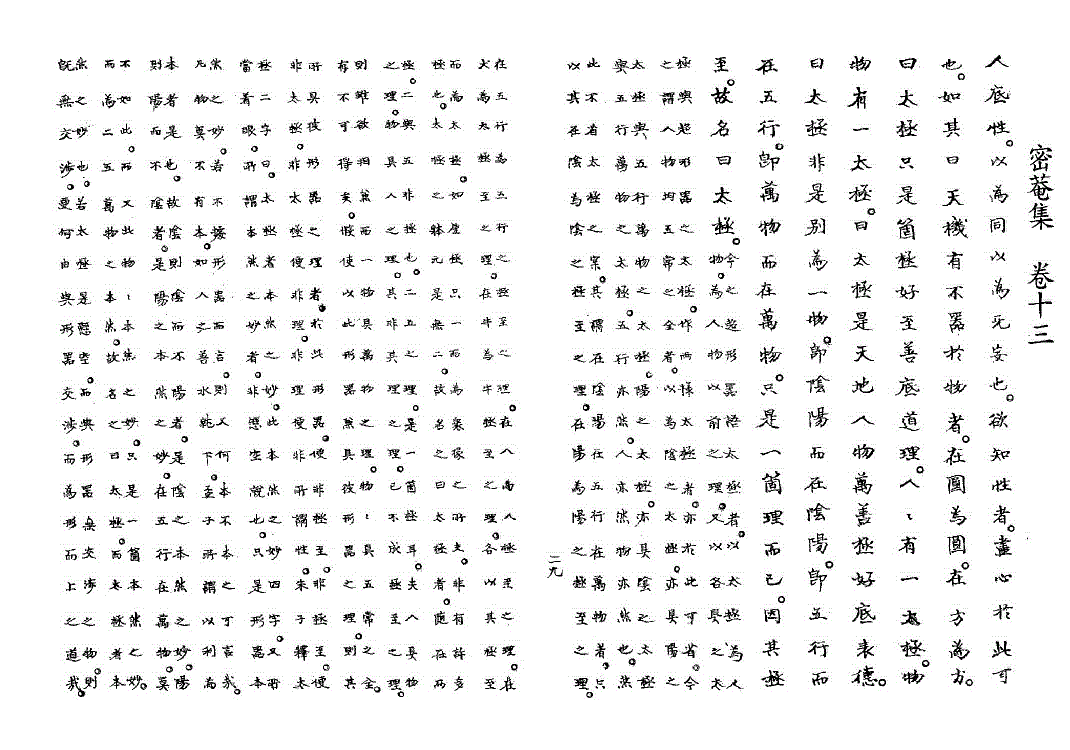 人底性。以为同以为无妄也。欲知性者。尽心于此可也。如其曰天机有不器于物者。在圆为圆。在方为方。曰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曰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极好底表德。曰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今之超形器语太极者。以太极为人物。为人物以前之理。又以各具之太极与超形器之太极。作两㨾太极者。亦于此可省。今之谓人物均五常之全者。以为阴之太极。亦具阳之太极与五行万物之太极。阳之太极。亦具阴之太极与五行万物之太极。五行亦然。人亦然物亦然也。然此不省太极之宲。其谓在阴阳在五行在万物者。只以其在阴为阴之极至之理。在阳为阳之极至之理。在五行为五行之极至之理。在人为人极至之理。在犬为太(一作犬)极至之理。在牛为牛极至之理。各以其极至而为太极。如屋极只一而为众椽之所支。非有许多极也。太极之体元是无二。故名之曰太极者。随在两极。二与五非极也。二五之理。是一个极耳。夫人具物之理。物具人之理。其非其理之理。已不成极至之理。则虽欲相兼而一物具万物之理。物物具五常之全。有不可得矣。假使以此形器兼具彼形器之理。则其所具彼形器之理者。于此形器。便非极至。非极至。便非太极。非太极便非理。非理便非所谓性。朱子释太极二字曰。太极者本然之妙。此本然之妙四字。又所当着眼。所谓本然之妙者。非悬空说也。只是形器本然之妙。若不据形器而言。则又何本不本之可言哉。凡物莫不有本。如人之善水就下。孟子所谓以利为本者是也。故阴则阴而不阳者。是阴之本然之妙。阳则阳而不阴者。是阳之本然之妙。在五行在万物。莫不如此。而又此物物本然之妙。只是一个本然之妙。而为二五万物之本然。故名之曰太极。而太极者本然之妙也。若太极是悬空。而与形器无交涉之物。则既无交涉。更何由与形器交涉。而为形而上之道哉。
人底性。以为同以为无妄也。欲知性者。尽心于此可也。如其曰天机有不器于物者。在圆为圆。在方为方。曰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曰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极好底表德。曰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今之超形器语太极者。以太极为人物。为人物以前之理。又以各具之太极与超形器之太极。作两㨾太极者。亦于此可省。今之谓人物均五常之全者。以为阴之太极。亦具阳之太极与五行万物之太极。阳之太极。亦具阴之太极与五行万物之太极。五行亦然。人亦然物亦然也。然此不省太极之宲。其谓在阴阳在五行在万物者。只以其在阴为阴之极至之理。在阳为阳之极至之理。在五行为五行之极至之理。在人为人极至之理。在犬为太(一作犬)极至之理。在牛为牛极至之理。各以其极至而为太极。如屋极只一而为众椽之所支。非有许多极也。太极之体元是无二。故名之曰太极者。随在两极。二与五非极也。二五之理。是一个极耳。夫人具物之理。物具人之理。其非其理之理。已不成极至之理。则虽欲相兼而一物具万物之理。物物具五常之全。有不可得矣。假使以此形器兼具彼形器之理。则其所具彼形器之理者。于此形器。便非极至。非极至。便非太极。非太极便非理。非理便非所谓性。朱子释太极二字曰。太极者本然之妙。此本然之妙四字。又所当着眼。所谓本然之妙者。非悬空说也。只是形器本然之妙。若不据形器而言。则又何本不本之可言哉。凡物莫不有本。如人之善水就下。孟子所谓以利为本者是也。故阴则阴而不阳者。是阴之本然之妙。阳则阳而不阴者。是阳之本然之妙。在五行在万物。莫不如此。而又此物物本然之妙。只是一个本然之妙。而为二五万物之本然。故名之曰太极。而太极者本然之妙也。若太极是悬空。而与形器无交涉之物。则既无交涉。更何由与形器交涉。而为形而上之道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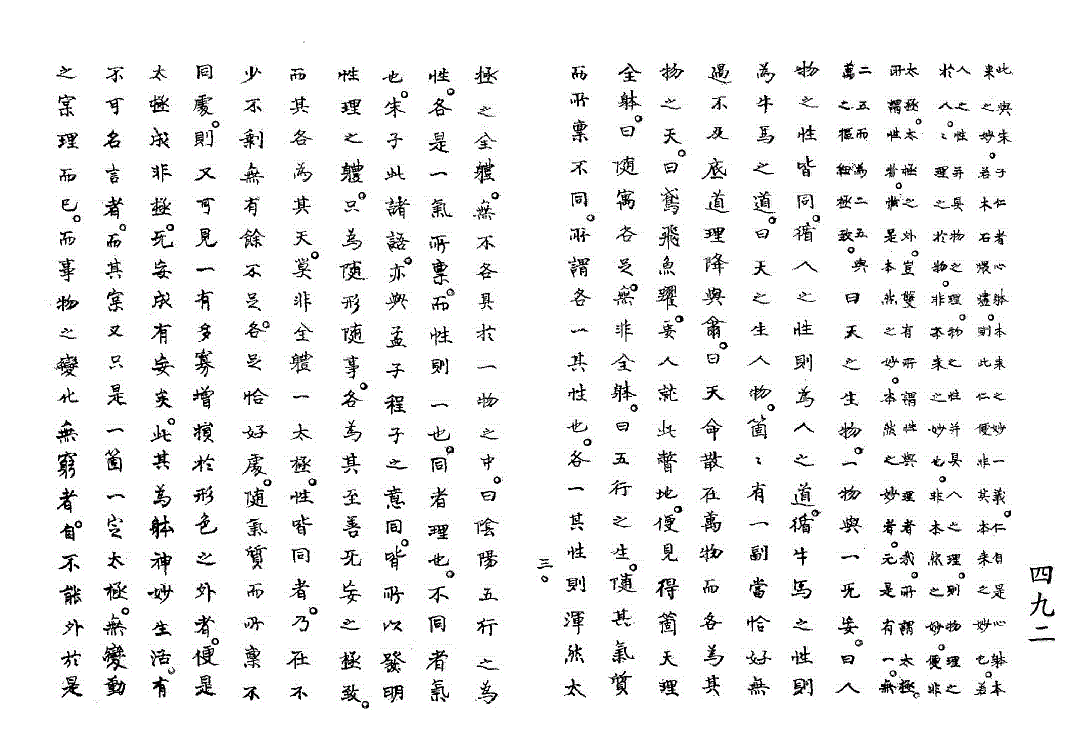 此与朱子仁者心体本来之妙一义。仁自是心体本来之妙。若木石煨烬。则此仁便非其本来之妙也。若人之性并具物之理。物之性并具人之理。则物理之于人。人理之于物。非本来之妙也。非本然之妙。便非太极。太极之外。岂双有所谓性与理者哉。所谓太极。所谓性者。惟是本然之妙。本然之妙者。元是有一。无二五而为二五与万之枢纽极致。 曰天之生物。一物与一无妄。曰人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则为人之道。循牛马之性则为牛马之道。曰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尔。曰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曰鸢飞鱼跃。要人就此瞥地。便见得个天理全体。曰随寓各足。无非全体。曰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曰阴阳五行之为性。各是一气所禀。而性则一也。同者理也。不同者气也。朱子此诸语。亦与孟子程子之意同。皆所以发明性理之体。只为随形随事。各为其至善无妄之极致。而其各为其天。莫非全体一太极。性皆同者。乃在不少不剩无有馀不足。各足恰好处。随气质而所禀不同处。则又可见一有多寡增损于形色之外者。便是太极成非极。无妄成有妄矣。此其为体神妙生活。有不可名言者。而其宲又只是一个一定太极。无变动之宲理而已。而事物之变化无穷者。自不能外于是
此与朱子仁者心体本来之妙一义。仁自是心体本来之妙。若木石煨烬。则此仁便非其本来之妙也。若人之性并具物之理。物之性并具人之理。则物理之于人。人理之于物。非本来之妙也。非本然之妙。便非太极。太极之外。岂双有所谓性与理者哉。所谓太极。所谓性者。惟是本然之妙。本然之妙者。元是有一。无二五而为二五与万之枢纽极致。 曰天之生物。一物与一无妄。曰人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则为人之道。循牛马之性则为牛马之道。曰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尔。曰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曰鸢飞鱼跃。要人就此瞥地。便见得个天理全体。曰随寓各足。无非全体。曰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曰阴阳五行之为性。各是一气所禀。而性则一也。同者理也。不同者气也。朱子此诸语。亦与孟子程子之意同。皆所以发明性理之体。只为随形随事。各为其至善无妄之极致。而其各为其天。莫非全体一太极。性皆同者。乃在不少不剩无有馀不足。各足恰好处。随气质而所禀不同处。则又可见一有多寡增损于形色之外者。便是太极成非极。无妄成有妄矣。此其为体神妙生活。有不可名言者。而其宲又只是一个一定太极。无变动之宲理而已。而事物之变化无穷者。自不能外于是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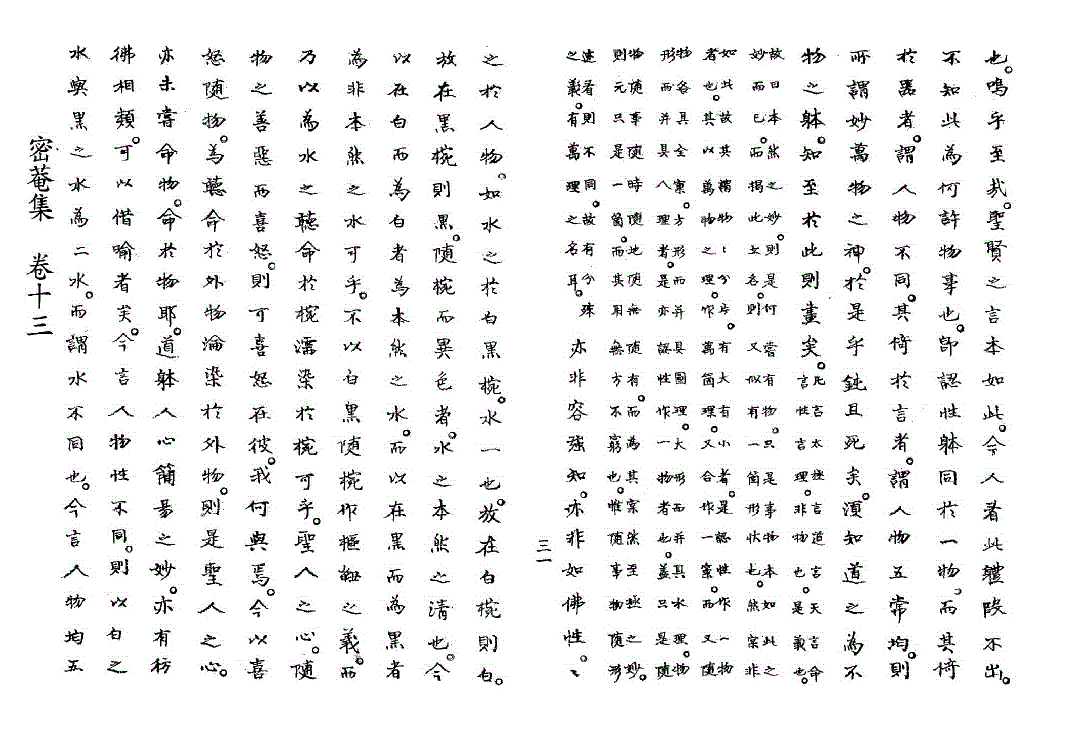 也。呜乎至哉。圣贤之言本如此。今人看此体段不出。不知此为何许物事也。即认性体同于一物。而其倚于器者。谓人物不同。其倚于言者。谓人物五常均。则所谓妙万物之神。于是乎钝且死矣。须知道之为不物之体。知至于此则尽矣。(凡言太极言道言天言命言性言理。非物也。是义也。故曰本然之妙。则是何尝有物。只是事物本如此之妙而已。而揭此立名。则又似有一个形状也。然宲非如此故其谓物物分片。有大有小者。是认性作一物者也。其以万物之理。作万个理。又合作一窠。而又随物各具全窠。方形而并具圆理。火形而并具水理。物形而并具人理者。是亦认性作一物者也。盖只是随物随事随时随地随无随有。而为其宲然至极之妙。则元只是一个。而其用无方不穷也。惟随事物随形迹看则不同。故有分殊之义。有万理之名耳。)亦非容强知。亦非如佛性。性之于人物。如水之于白黑碗。水一也。放在白碗则白。放在黑碗则黑。随碗而异色者。水之本然之清也。今以在白而为白者为本然之水。而以在黑而为黑者为非本然之水可乎。不以白黑随碗作枢纽之义。而乃以为水之听命于碗濡染于碗可乎。圣人之心。随物之善恶而喜怒。则可喜怒在彼。我何与焉。今以喜怒随物。为听命于外物沦染于外物。则是圣人之心。亦未尝命物。命于物耶。道体人心简易之妙。亦有彷佛相类。可以借喻者矣。今言人物性不同。则以白之水与黑之水为二水。而谓水不同也。今言人物均五
也。呜乎至哉。圣贤之言本如此。今人看此体段不出。不知此为何许物事也。即认性体同于一物。而其倚于器者。谓人物不同。其倚于言者。谓人物五常均。则所谓妙万物之神。于是乎钝且死矣。须知道之为不物之体。知至于此则尽矣。(凡言太极言道言天言命言性言理。非物也。是义也。故曰本然之妙。则是何尝有物。只是事物本如此之妙而已。而揭此立名。则又似有一个形状也。然宲非如此故其谓物物分片。有大有小者。是认性作一物者也。其以万物之理。作万个理。又合作一窠。而又随物各具全窠。方形而并具圆理。火形而并具水理。物形而并具人理者。是亦认性作一物者也。盖只是随物随事随时随地随无随有。而为其宲然至极之妙。则元只是一个。而其用无方不穷也。惟随事物随形迹看则不同。故有分殊之义。有万理之名耳。)亦非容强知。亦非如佛性。性之于人物。如水之于白黑碗。水一也。放在白碗则白。放在黑碗则黑。随碗而异色者。水之本然之清也。今以在白而为白者为本然之水。而以在黑而为黑者为非本然之水可乎。不以白黑随碗作枢纽之义。而乃以为水之听命于碗濡染于碗可乎。圣人之心。随物之善恶而喜怒。则可喜怒在彼。我何与焉。今以喜怒随物。为听命于外物沦染于外物。则是圣人之心。亦未尝命物。命于物耶。道体人心简易之妙。亦有彷佛相类。可以借喻者矣。今言人物性不同。则以白之水与黑之水为二水。而谓水不同也。今言人物均五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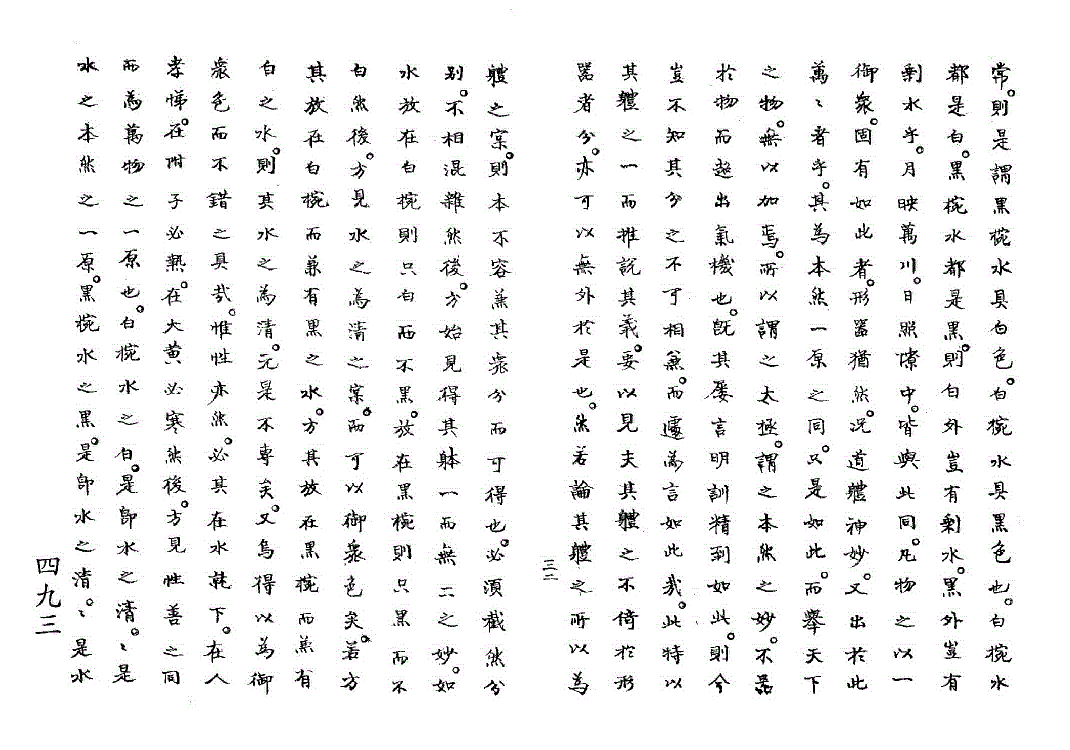 常。则是谓黑碗水具白色。白碗水具黑色也。白碗水都是白。黑碗水都是黑。则白外岂有剩水。黑外岂有剩水乎。月映万川。日照隙中。皆与此同。凡物之以一御众。固有如此者。形器犹然。况道体神妙。又出于此万万者乎。其为本然一原之同。只是如此。而举天下之物。无以加焉。所以谓之太极。谓之本然之妙。不器于物而超出气机也。既其屡言明训精到如此。则今岂不知其分之不可相兼。而遽为言如此哉。此特以其体之一而推说其义。要以见夫其体之不倚于形器者分。亦可以无外于是也。然若论其体之所以为体之宲。则本不容兼其众分而可得也。必须截然分别。不相混杂然后。方始见得其体一而无二之妙。如水放在白碗则只白而不黑。放在黑碗则只黑而不白然后。方见水之为清之宲。而可以御众色矣。若方其放在白碗而兼有黑之水。方其放在黑碗而兼有白之水。则其水之为清。元是不专矣。又乌得以为御众色而不错之具哉。惟性亦然。必其在水就下。在人孝悌。在附子必热。在大黄必寒然后。方见性善之同而为万物之一原也。白碗水之白。是即水之清。清是水之本然之一原。黑碗水之黑。是即水之清。清是水
常。则是谓黑碗水具白色。白碗水具黑色也。白碗水都是白。黑碗水都是黑。则白外岂有剩水。黑外岂有剩水乎。月映万川。日照隙中。皆与此同。凡物之以一御众。固有如此者。形器犹然。况道体神妙。又出于此万万者乎。其为本然一原之同。只是如此。而举天下之物。无以加焉。所以谓之太极。谓之本然之妙。不器于物而超出气机也。既其屡言明训精到如此。则今岂不知其分之不可相兼。而遽为言如此哉。此特以其体之一而推说其义。要以见夫其体之不倚于形器者分。亦可以无外于是也。然若论其体之所以为体之宲。则本不容兼其众分而可得也。必须截然分别。不相混杂然后。方始见得其体一而无二之妙。如水放在白碗则只白而不黑。放在黑碗则只黑而不白然后。方见水之为清之宲。而可以御众色矣。若方其放在白碗而兼有黑之水。方其放在黑碗而兼有白之水。则其水之为清。元是不专矣。又乌得以为御众色而不错之具哉。惟性亦然。必其在水就下。在人孝悌。在附子必热。在大黄必寒然后。方见性善之同而为万物之一原也。白碗水之白。是即水之清。清是水之本然之一原。黑碗水之黑。是即水之清。清是水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4H 页
 之本然之一原。犬之吠。是即性之一原。牛之耕。是即性之一原。人之仁义。是即性之一原。附子之热。大黄之寒。是即性之一原。水何尝离其色之异。而有清之一原。性何尝离人物之异。而有善之一原哉。凡曰道曰理者。自是由其有路脉有条理。不相淆乱而言。而自有其体一而贯之也。今以其众分之为一体所统。而遂谓其体之所在分无不具者。以物言则语势似当如此。而道之宲体不物则不如此。故只为推说则可。不得为正义也。不但论性如此。凡论理皆如此。今于此不会辨别。(如物理从来齐。物形从来不齐。同者理。不同者气之语。若不知其意脉。则并作一物之中。具万物之理。自无怪。然其谓齐谓同者。不如此说。须知理同气异。又须知理之同。不是局定底。其各为其物之理者。乃所以为同。不是于一物之中。具万物之理以为同。而不具万物之理时。却成不同也。其谓齐谓同者。自非强说。亦非虚名。姑为此题目也。元来是宲然之妙体。无容口舌。须亲见得众理之体是如何物事。则见得多后。自当有豁然贯通。而方见其所谓齐所谓同之本意。初非谓件数之均也。)乃以其推说之语。反作正义。而其论性同。必以各具全分为言者。此以体一分殊分本末之义。混看作形质资质分本末之义也。体一分殊之本末。理上分也。形质资质之本末。气上分也。体一分殊之义。如程子所谓理无大小。道无精粗。贯通只一理。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事物有精粗大小本末之异。而理则只一以贯通。无分于事物之精粗大小本
之本然之一原。犬之吠。是即性之一原。牛之耕。是即性之一原。人之仁义。是即性之一原。附子之热。大黄之寒。是即性之一原。水何尝离其色之异。而有清之一原。性何尝离人物之异。而有善之一原哉。凡曰道曰理者。自是由其有路脉有条理。不相淆乱而言。而自有其体一而贯之也。今以其众分之为一体所统。而遂谓其体之所在分无不具者。以物言则语势似当如此。而道之宲体不物则不如此。故只为推说则可。不得为正义也。不但论性如此。凡论理皆如此。今于此不会辨别。(如物理从来齐。物形从来不齐。同者理。不同者气之语。若不知其意脉。则并作一物之中。具万物之理。自无怪。然其谓齐谓同者。不如此说。须知理同气异。又须知理之同。不是局定底。其各为其物之理者。乃所以为同。不是于一物之中。具万物之理以为同。而不具万物之理时。却成不同也。其谓齐谓同者。自非强说。亦非虚名。姑为此题目也。元来是宲然之妙体。无容口舌。须亲见得众理之体是如何物事。则见得多后。自当有豁然贯通。而方见其所谓齐所谓同之本意。初非谓件数之均也。)乃以其推说之语。反作正义。而其论性同。必以各具全分为言者。此以体一分殊分本末之义。混看作形质资质分本末之义也。体一分殊之本末。理上分也。形质资质之本末。气上分也。体一分殊之义。如程子所谓理无大小。道无精粗。贯通只一理。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事物有精粗大小本末之异。而理则只一以贯通。无分于事物之精粗大小本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4L 页
 末云。此言理之体妙众物而为一之义。)如朱子所谓惟其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密察于区别之中。见得其本无二致。小处大处。都是理事之大小固不同。然以理言。则未尝有大小之间而无不在。二者之理只一般。事有大小。理无精粗。自形而下者言。则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语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则未尝有馀于此。不足于彼。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是一㨾道理合起来。便是道之全体。非大底是全体。小底不是全体。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说仁则都在仁上。说诚则都在诚上。凡此类皆于事物不同上。要见得理之体一而无二。朱子言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栗谷言本然者理之一。盖理之一处。是于理为体而为本也。其体之一者为本。则其分之随气不齐。而谓之万理谓之万象者。乃为其末矣。此则于理上。分体一分殊为本末者也。(此本末字。与分本末为两端之本末不同。)孔子所谓物与无妄,神妙万物,同归一致,同而异,一以贯之。皆此体一之义也。如程子所谓性则理也。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其性之本。张子所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
末云。此言理之体妙众物而为一之义。)如朱子所谓惟其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密察于区别之中。见得其本无二致。小处大处。都是理事之大小固不同。然以理言。则未尝有大小之间而无不在。二者之理只一般。事有大小。理无精粗。自形而下者言。则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语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则未尝有馀于此。不足于彼。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是一㨾道理合起来。便是道之全体。非大底是全体。小底不是全体。理只是一个理。理举着全无欠阙。说仁则都在仁上。说诚则都在诚上。凡此类皆于事物不同上。要见得理之体一而无二。朱子言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栗谷言本然者理之一。盖理之一处。是于理为体而为本也。其体之一者为本。则其分之随气不齐。而谓之万理谓之万象者。乃为其末矣。此则于理上。分体一分殊为本末者也。(此本末字。与分本末为两端之本末不同。)孔子所谓物与无妄,神妙万物,同归一致,同而异,一以贯之。皆此体一之义也。如程子所谓性则理也。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其性之本。张子所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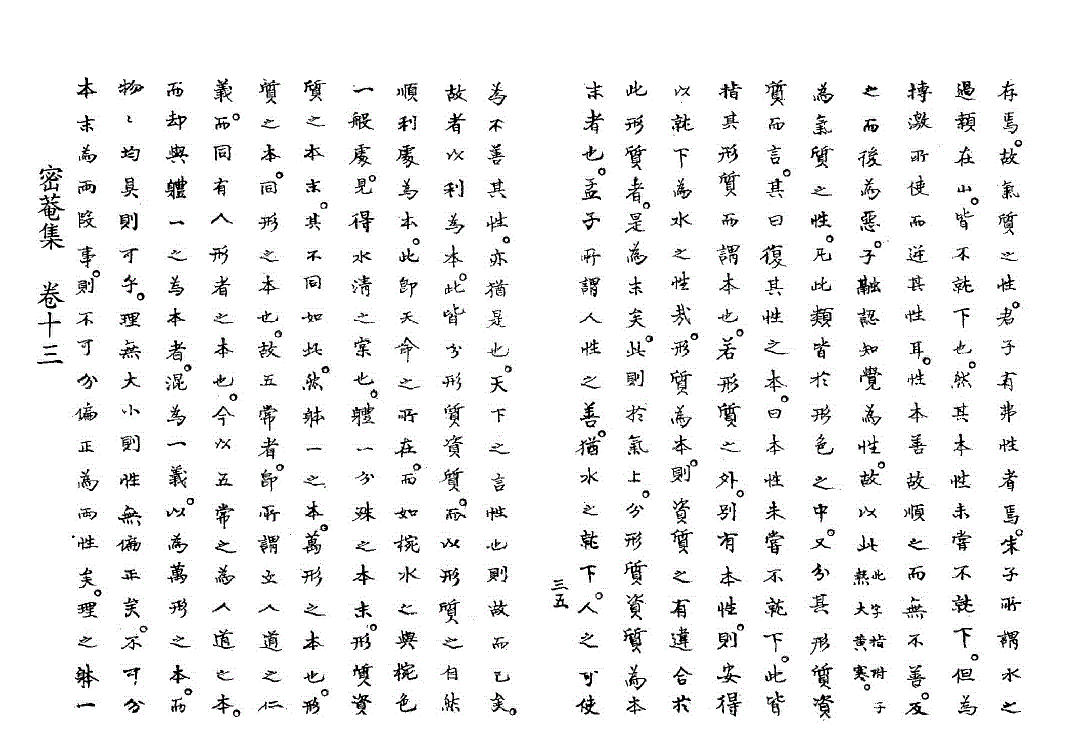 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所谓水之过颡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尝不就下。但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反之而后为恶。子融认知觉为性。故以此(此字指附子热大黄寒。)为气质之性。凡此类皆于形色之中。又分其形质资质而言。其曰复其性之本。曰本性未尝不就下。此皆指其形质而谓本也。若形质之外。别有本性。则安得以就下为水之性哉。形质为本。则资质之有违合于此形质者。是为末矣。此则于气上。分形质资质为本末者也。孟子所谓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此皆分形质资质。而以形质之自然顺利处为本。此即天命之所在。而如碗水之与碗色一般处。见得水清之宲也。体一分殊之本末。形质资质之本末。其不同如此。然体一之本。万形之本也。形质之本。同形之本也。故五常者。即所谓立人道之仁义。而同有人形者之本也。今以五常之为人道之本。而却与体一之为本者。混为一义。以为万形之本。而物物均具则可乎。理无大小则性无偏正矣。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则不可分偏正为两性矣。理之体一
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所谓水之过颡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尝不就下。但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反之而后为恶。子融认知觉为性。故以此(此字指附子热大黄寒。)为气质之性。凡此类皆于形色之中。又分其形质资质而言。其曰复其性之本。曰本性未尝不就下。此皆指其形质而谓本也。若形质之外。别有本性。则安得以就下为水之性哉。形质为本。则资质之有违合于此形质者。是为末矣。此则于气上。分形质资质为本末者也。孟子所谓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此皆分形质资质。而以形质之自然顺利处为本。此即天命之所在。而如碗水之与碗色一般处。见得水清之宲也。体一分殊之本末。形质资质之本末。其不同如此。然体一之本。万形之本也。形质之本。同形之本也。故五常者。即所谓立人道之仁义。而同有人形者之本也。今以五常之为人道之本。而却与体一之为本者。混为一义。以为万形之本。而物物均具则可乎。理无大小则性无偏正矣。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则不可分偏正为两性矣。理之体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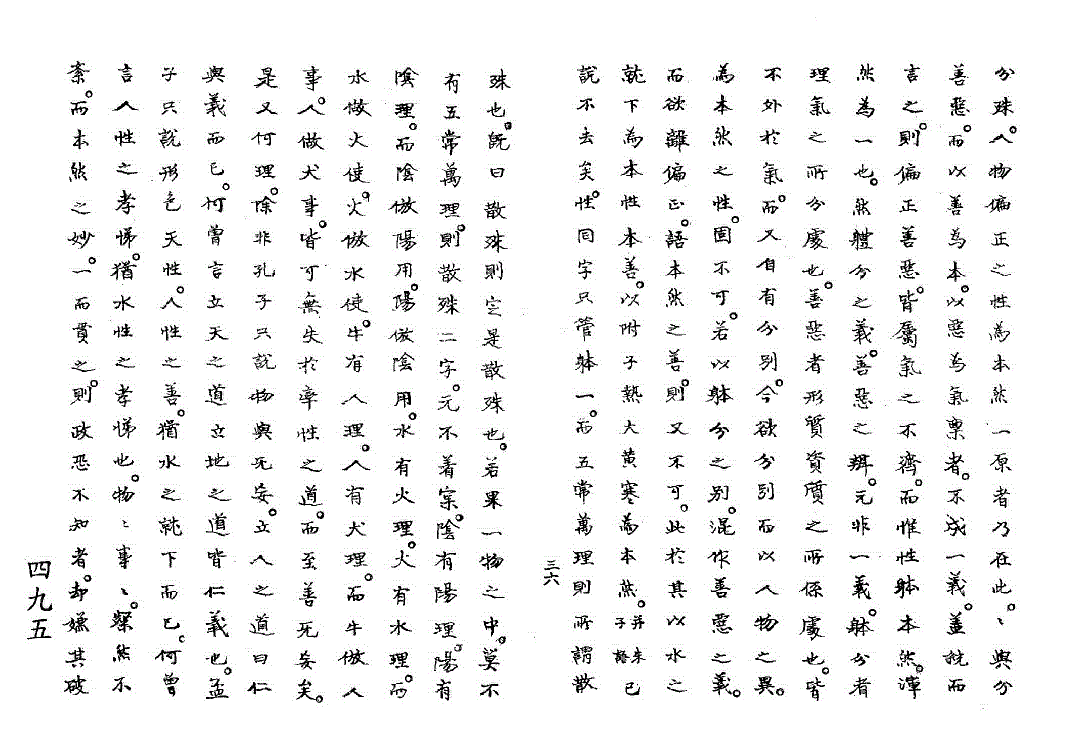 分殊。人物偏正之性为本然一原者乃在此。此与分善恶。而以善为本。以恶为气禀者。不成一义。盖统而言之。则偏正善恶。皆属气之不齐。而惟性体本然。浑然为一也。然体分之义。善恶之辨。元非一义。体分者理气之所分处也。善恶者形质资质之所系处也。皆不外于气。而又自有分别。今欲分别而以人物之异。为本然之性。固不可。若以体分之别。混作善恶之义。而欲离偏正。语本然之善。则又不可。此于其以水之就下为本性本善。以附子热大黄寒为本然。(并朱子语)已说不去矣。性同字只管体一。而五常万理则所谓散殊也。既曰散殊则定是散殊也。若果一物之中。莫不有五常万理。则散殊二字。元不着宲。阴有阳理。阳有阴理。而阴仿阳用。阳仿阴用。水有火理。火有水理。而水做火使。火仿水使。牛有人理。人有犬理。而牛仿人事。人做犬事。皆可无失于率性之道。而至善无妄矣。是又何理。除非孔子只说物与无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已。何曾言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皆仁义也。孟子只说形色天性。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而已。何曾言人性之孝悌。犹水性之孝悌也。物物事事。粲然不紊。而本然之妙。一而贯之。则政恐不知者。却嫌其破
分殊。人物偏正之性为本然一原者乃在此。此与分善恶。而以善为本。以恶为气禀者。不成一义。盖统而言之。则偏正善恶。皆属气之不齐。而惟性体本然。浑然为一也。然体分之义。善恶之辨。元非一义。体分者理气之所分处也。善恶者形质资质之所系处也。皆不外于气。而又自有分别。今欲分别而以人物之异。为本然之性。固不可。若以体分之别。混作善恶之义。而欲离偏正。语本然之善。则又不可。此于其以水之就下为本性本善。以附子热大黄寒为本然。(并朱子语)已说不去矣。性同字只管体一。而五常万理则所谓散殊也。既曰散殊则定是散殊也。若果一物之中。莫不有五常万理。则散殊二字。元不着宲。阴有阳理。阳有阴理。而阴仿阳用。阳仿阴用。水有火理。火有水理。而水做火使。火仿水使。牛有人理。人有犬理。而牛仿人事。人做犬事。皆可无失于率性之道。而至善无妄矣。是又何理。除非孔子只说物与无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已。何曾言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皆仁义也。孟子只说形色天性。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而已。何曾言人性之孝悌。犹水性之孝悌也。物物事事。粲然不紊。而本然之妙。一而贯之。则政恐不知者。却嫌其破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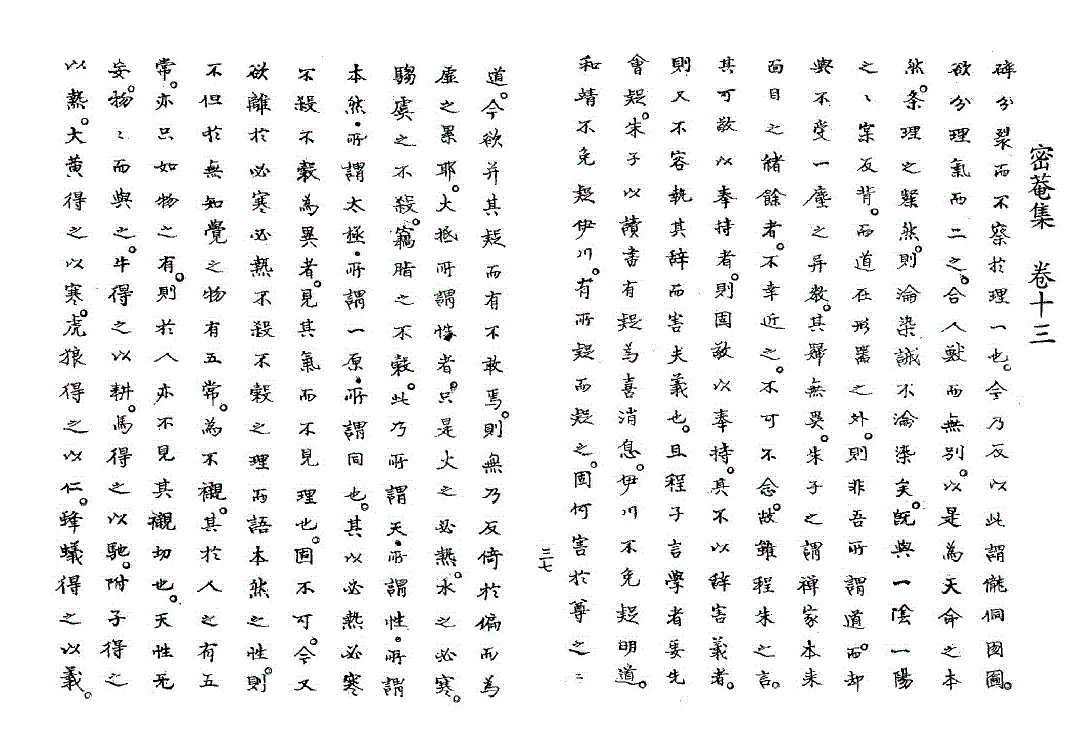 碎分裂而不察于理一也。今乃反以此谓儱侗囫囵。欲分理气而二之。合人兽而无别。以是为天命之本然。条理之粲然。则沦染诚不沦染矣。既与一阴一阳之之宲反背。而道在形器之外。则非吾所谓道。而却与不受一尘之异教。其归无异。朱子之谓禅家本来面目之绪馀者。不幸近之。不可不念。故虽程朱之言。其可敬以奉持者。则固敬以奉持。其不以辞害义者。则又不容执其辞而害夫义也。且程子言学者要先会疑。朱子以读书有疑为喜消息。伊川不免疑明道。和靖不免疑伊川。有所疑而疑之。固何害于尊之之道。今欲并其疑而有不敢焉。则无乃反倚于偏而为虚之累耶。大抵所谓性者。只是火之必热。水之必寒。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乃所谓天,所谓性,所谓本然,所谓太极,所谓一原,所谓同也。其以必热必寒不杀不谷为异者。见其气而不见理也。固不可。今又欲离于必寒必热不杀不谷之理而语本然之性。则不但于无知觉之物有五常。为不衬。其于人之有五常。亦只如物之有。则于人亦不见其衬切也。天性无妄。物物而与之。牛得之以耕。马得之以驰。附子得之以热。大黄得之以寒。虎狼得之以仁。蜂蚁得之以义。
碎分裂而不察于理一也。今乃反以此谓儱侗囫囵。欲分理气而二之。合人兽而无别。以是为天命之本然。条理之粲然。则沦染诚不沦染矣。既与一阴一阳之之宲反背。而道在形器之外。则非吾所谓道。而却与不受一尘之异教。其归无异。朱子之谓禅家本来面目之绪馀者。不幸近之。不可不念。故虽程朱之言。其可敬以奉持者。则固敬以奉持。其不以辞害义者。则又不容执其辞而害夫义也。且程子言学者要先会疑。朱子以读书有疑为喜消息。伊川不免疑明道。和靖不免疑伊川。有所疑而疑之。固何害于尊之之道。今欲并其疑而有不敢焉。则无乃反倚于偏而为虚之累耶。大抵所谓性者。只是火之必热。水之必寒。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乃所谓天,所谓性,所谓本然,所谓太极,所谓一原,所谓同也。其以必热必寒不杀不谷为异者。见其气而不见理也。固不可。今又欲离于必寒必热不杀不谷之理而语本然之性。则不但于无知觉之物有五常。为不衬。其于人之有五常。亦只如物之有。则于人亦不见其衬切也。天性无妄。物物而与之。牛得之以耕。马得之以驰。附子得之以热。大黄得之以寒。虎狼得之以仁。蜂蚁得之以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6L 页
 人得之以仁义。草木土石得之以贲若柔刚。正气得之以正。偏气得之以偏。性则耕于牛者。即驰于马者也。热于附子者。即寒于大黄者也。仁义于知觉者。即柔刚于土石者也。正于正气者。即偏于偏气者也。非一而可乎。非同而可乎。然牛之所以耕。而马既以之驰。则其驰之性。即牛耕之性也。今谓驰之上。而又有耕之性可乎。附子之所以热。而大黄既以之寒。则其寒之性。即附子热之性也。今谓寒之上。而又有热之性可乎。知觉之所以仁义。而土石既以之柔刚。则其柔刚之性。即人仁义之性也。今谓柔刚之上。而又有仁义之性可乎。正气之所以正也。而偏气既以之偏。则其偏之性。即正之性也。今谓偏之上。而又有正之性可乎。既皆以无妄之天性。而各正其性矣。今欲舍其各正之性。而别有天性可乎。耕驰寒热仁义柔刚正偏不同。而性则同一无妄也。今谓性一性同足矣。又谓耕驰之中。而寒热仁义之性莫不有。柔刚之中。而仁义之性莫不有。偏之中。而正之性莫不有。莫不有然后性一。则有不有者。非性一也。是为识性乎。为不识性乎。程子曰无妄天性。天性岂有妄耶。耕于牛为无妄。而于马则妄矣。热于附子为无妄。而于大黄
人得之以仁义。草木土石得之以贲若柔刚。正气得之以正。偏气得之以偏。性则耕于牛者。即驰于马者也。热于附子者。即寒于大黄者也。仁义于知觉者。即柔刚于土石者也。正于正气者。即偏于偏气者也。非一而可乎。非同而可乎。然牛之所以耕。而马既以之驰。则其驰之性。即牛耕之性也。今谓驰之上。而又有耕之性可乎。附子之所以热。而大黄既以之寒。则其寒之性。即附子热之性也。今谓寒之上。而又有热之性可乎。知觉之所以仁义。而土石既以之柔刚。则其柔刚之性。即人仁义之性也。今谓柔刚之上。而又有仁义之性可乎。正气之所以正也。而偏气既以之偏。则其偏之性。即正之性也。今谓偏之上。而又有正之性可乎。既皆以无妄之天性。而各正其性矣。今欲舍其各正之性。而别有天性可乎。耕驰寒热仁义柔刚正偏不同。而性则同一无妄也。今谓性一性同足矣。又谓耕驰之中。而寒热仁义之性莫不有。柔刚之中。而仁义之性莫不有。偏之中。而正之性莫不有。莫不有然后性一。则有不有者。非性一也。是为识性乎。为不识性乎。程子曰无妄天性。天性岂有妄耶。耕于牛为无妄。而于马则妄矣。热于附子为无妄。而于大黄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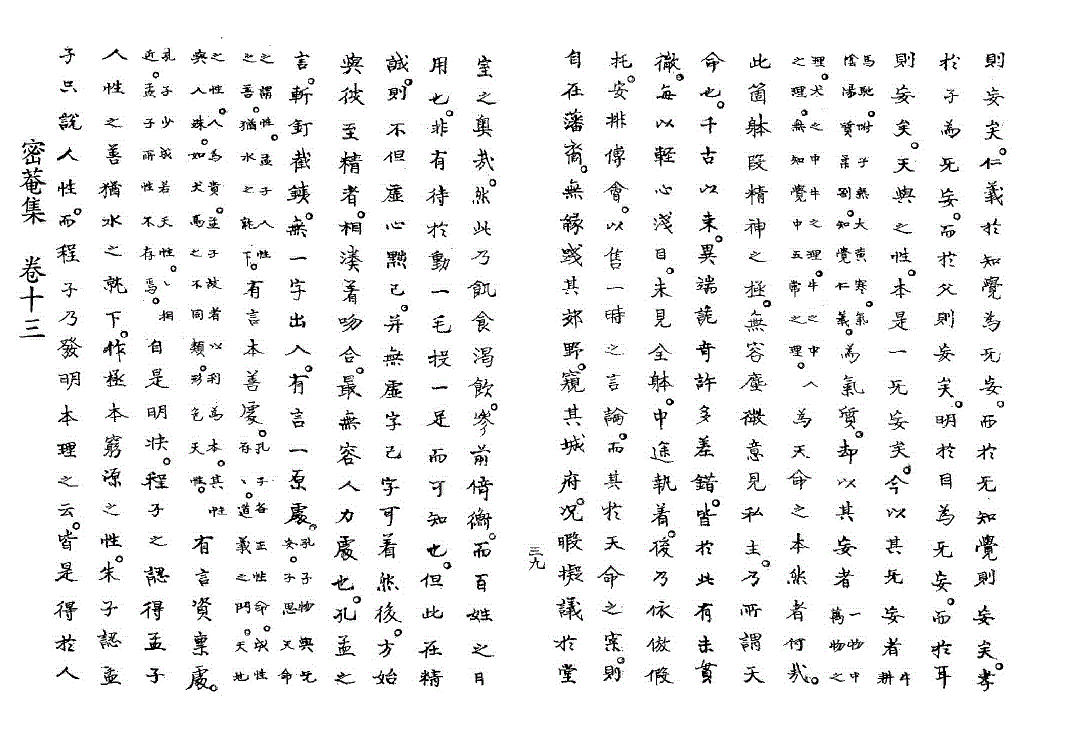 则妄矣。仁义于知觉为无妄。而于无知觉则妄矣。孝于子为无妄。而于父则妄矣。明于目为无妄。而于耳则妄矣。天与之性。本是一无妄矣。今以其无妄者(牛耕马驰。附子热大黄寒。气阴阳质柔刚。知觉仁义。)为气质。却以其妄者(一物中万物之理。犬之中牛之理。牛之中人之理。无知觉中五常之理。)为天命之本然者何哉。此个体段精神之极。无容尘微意见私主。乃所谓天命也。千古以来。异端诡奇许多差错。皆于此有未贯彻。每以轻心浅目。未见全体。中途执着。后乃依仿假托。安排傅会。以售一时之言论。而其于天命之宲。则自在藩裔。无缘践其郊野。窥其城府。况暇拟议于堂室之奥哉。然此乃饥食渴饮。参前倚衡。而百姓之日用也。非有待于动一毛投一足而可知也。但此在精诚。则不但虚心黜己。并无虚字己字可着然后。方始与彼至精者。相凑着吻合。最无容人力处也。孔孟之言。斩钉截铁。无一字出入。有言一原处。(孔子物与无妄。子思天命之谓性。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有言本善处。(孔子各正性命。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故者以利为本。其性与人殊。如犬马之不同类。形色天性。)有言资禀处。(孔子少成若天性。性相近。孟子所性不存焉。)自是明快。程子之认得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作极本穷源之性。朱子认孟子只说人性。而程子乃发明本理之云。皆是得于人
则妄矣。仁义于知觉为无妄。而于无知觉则妄矣。孝于子为无妄。而于父则妄矣。明于目为无妄。而于耳则妄矣。天与之性。本是一无妄矣。今以其无妄者(牛耕马驰。附子热大黄寒。气阴阳质柔刚。知觉仁义。)为气质。却以其妄者(一物中万物之理。犬之中牛之理。牛之中人之理。无知觉中五常之理。)为天命之本然者何哉。此个体段精神之极。无容尘微意见私主。乃所谓天命也。千古以来。异端诡奇许多差错。皆于此有未贯彻。每以轻心浅目。未见全体。中途执着。后乃依仿假托。安排傅会。以售一时之言论。而其于天命之宲。则自在藩裔。无缘践其郊野。窥其城府。况暇拟议于堂室之奥哉。然此乃饥食渴饮。参前倚衡。而百姓之日用也。非有待于动一毛投一足而可知也。但此在精诚。则不但虚心黜己。并无虚字己字可着然后。方始与彼至精者。相凑着吻合。最无容人力处也。孔孟之言。斩钉截铁。无一字出入。有言一原处。(孔子物与无妄。子思天命之谓性。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有言本善处。(孔子各正性命。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故者以利为本。其性与人殊。如犬马之不同类。形色天性。)有言资禀处。(孔子少成若天性。性相近。孟子所性不存焉。)自是明快。程子之认得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作极本穷源之性。朱子认孟子只说人性。而程子乃发明本理之云。皆是得于人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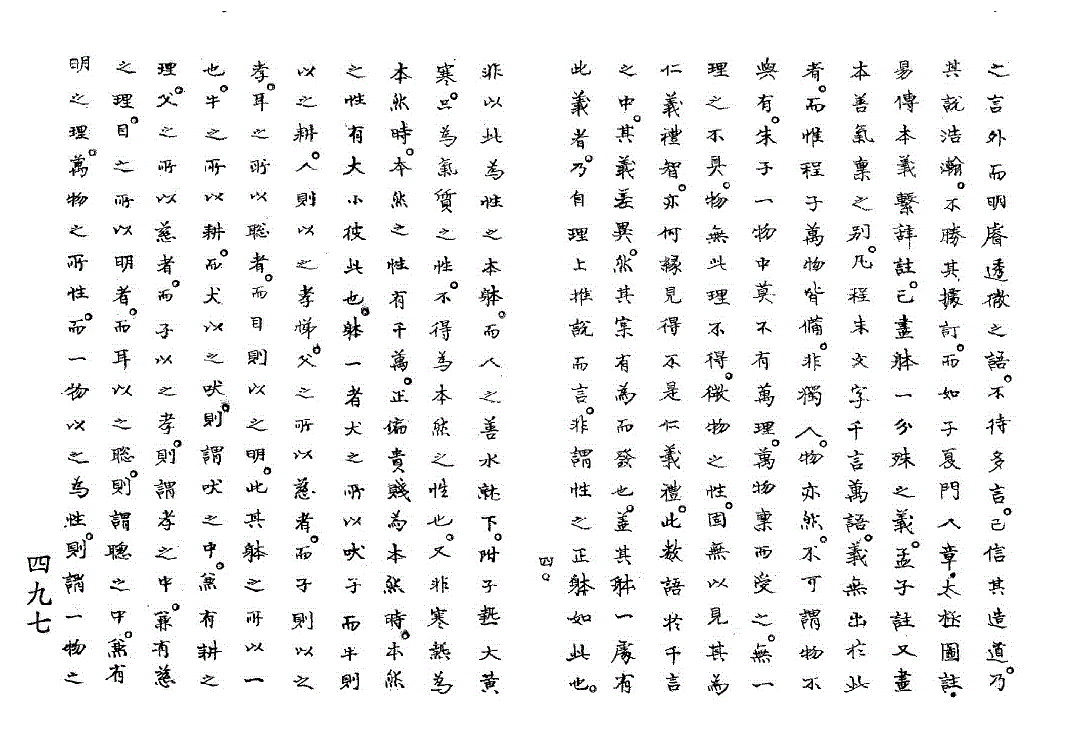 之言外而明睿透彻之语。不待多言。已信其造道。乃其说浩瀚。不胜其据订。而如子夏门人章,太极图注,易传本义系辞注。已尽体一分殊之义。孟子注又尽本善气禀之别。凡程朱文字千言万语。义无出于此者。而惟程子万物皆备。非独人。物亦然。不可谓物不与有。朱子一物中莫不有万理。万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物无此理不得。微物之性。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此数语于千言之中。其义差异。然其宲有为而发也。盖其体一处有此义者。乃自理上推说而言。非谓性之正体如此也。非以此为性之本体。而人之善水就下。附子热大黄寒。只为气质之性。不得为本然之性也。又非寒热为本然时。本然之性有千万。正偏贵贱为本然时。本然之性有大小彼此也。体一者犬之所以吠子而牛则以之耕。人则以之孝悌。父之所以慈者。而子则以之孝。耳之所以聪者。而目则以之明。此其体之所以一也。牛之所以耕。而犬以之吠。则谓吠之中。兼有耕之理。父之所以慈者。而子以之孝。则谓孝之中。兼有慈之理。目之所以明者。而耳以之聪。则谓聪之中。兼有明之理。万物之所性。而一物以之为性。则谓一物之
之言外而明睿透彻之语。不待多言。已信其造道。乃其说浩瀚。不胜其据订。而如子夏门人章,太极图注,易传本义系辞注。已尽体一分殊之义。孟子注又尽本善气禀之别。凡程朱文字千言万语。义无出于此者。而惟程子万物皆备。非独人。物亦然。不可谓物不与有。朱子一物中莫不有万理。万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物无此理不得。微物之性。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此数语于千言之中。其义差异。然其宲有为而发也。盖其体一处有此义者。乃自理上推说而言。非谓性之正体如此也。非以此为性之本体。而人之善水就下。附子热大黄寒。只为气质之性。不得为本然之性也。又非寒热为本然时。本然之性有千万。正偏贵贱为本然时。本然之性有大小彼此也。体一者犬之所以吠子而牛则以之耕。人则以之孝悌。父之所以慈者。而子则以之孝。耳之所以聪者。而目则以之明。此其体之所以一也。牛之所以耕。而犬以之吠。则谓吠之中。兼有耕之理。父之所以慈者。而子以之孝。则谓孝之中。兼有慈之理。目之所以明者。而耳以之聪。则谓聪之中。兼有明之理。万物之所性。而一物以之为性。则谓一物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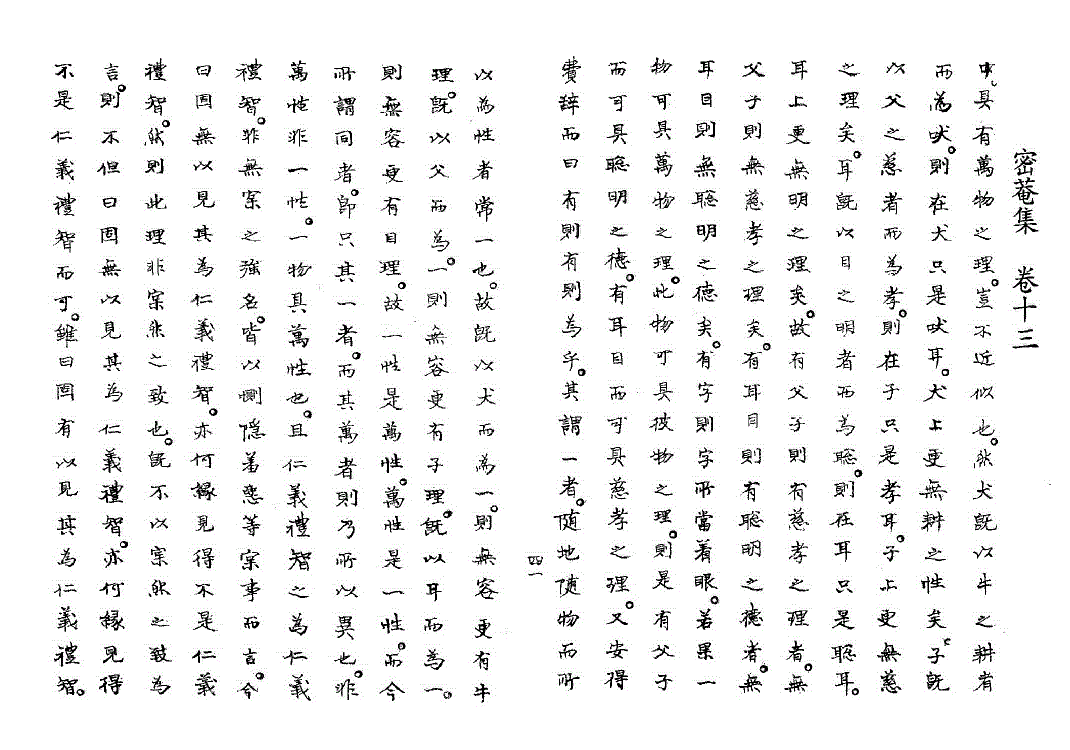 中。具有万物之理。岂不近似也。然犬既以牛之耕者而为吠。则在犬只是吠耳。犬上更无耕之性矣。子既以父之慈者而为孝。则在子只是孝耳。子上更无慈之理矣。耳既以目之明者而为聪。则在耳只是聪耳。耳上更无明之理矣。故有父子则有慈孝之理者。无父子则无慈孝之理矣。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者。无耳目则无聪明之德矣。有字则字所当着眼。若果一物可具万物之理。此物可具彼物之理。则是有父子而可具聪明之德。有耳目而可具慈孝之理。又安得费辞而曰有则有则为乎。其谓一者。随地随物而所以为性者常一也。故既以犬而为一。则无容更有牛理。既以父而为一。则无容更有子理。既以耳而为一。则无容更有目理。故一性是万性。万性是一性。而今所谓同者。即只其一者。而其万者则乃所以异也。非万性非一性。一物具万性也。且仁义礼智之为仁义礼智。非无宲之强名。皆以恻隐羞恶等宲事而言。今曰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智。然则此理非宲然之致也。既不以宲然之致为言。则不但曰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智而可。虽曰固有以见其为仁义礼智。
中。具有万物之理。岂不近似也。然犬既以牛之耕者而为吠。则在犬只是吠耳。犬上更无耕之性矣。子既以父之慈者而为孝。则在子只是孝耳。子上更无慈之理矣。耳既以目之明者而为聪。则在耳只是聪耳。耳上更无明之理矣。故有父子则有慈孝之理者。无父子则无慈孝之理矣。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者。无耳目则无聪明之德矣。有字则字所当着眼。若果一物可具万物之理。此物可具彼物之理。则是有父子而可具聪明之德。有耳目而可具慈孝之理。又安得费辞而曰有则有则为乎。其谓一者。随地随物而所以为性者常一也。故既以犬而为一。则无容更有牛理。既以父而为一。则无容更有子理。既以耳而为一。则无容更有目理。故一性是万性。万性是一性。而今所谓同者。即只其一者。而其万者则乃所以异也。非万性非一性。一物具万性也。且仁义礼智之为仁义礼智。非无宲之强名。皆以恻隐羞恶等宲事而言。今曰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智。然则此理非宲然之致也。既不以宲然之致为言。则不但曰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智而可。虽曰固有以见其为仁义礼智。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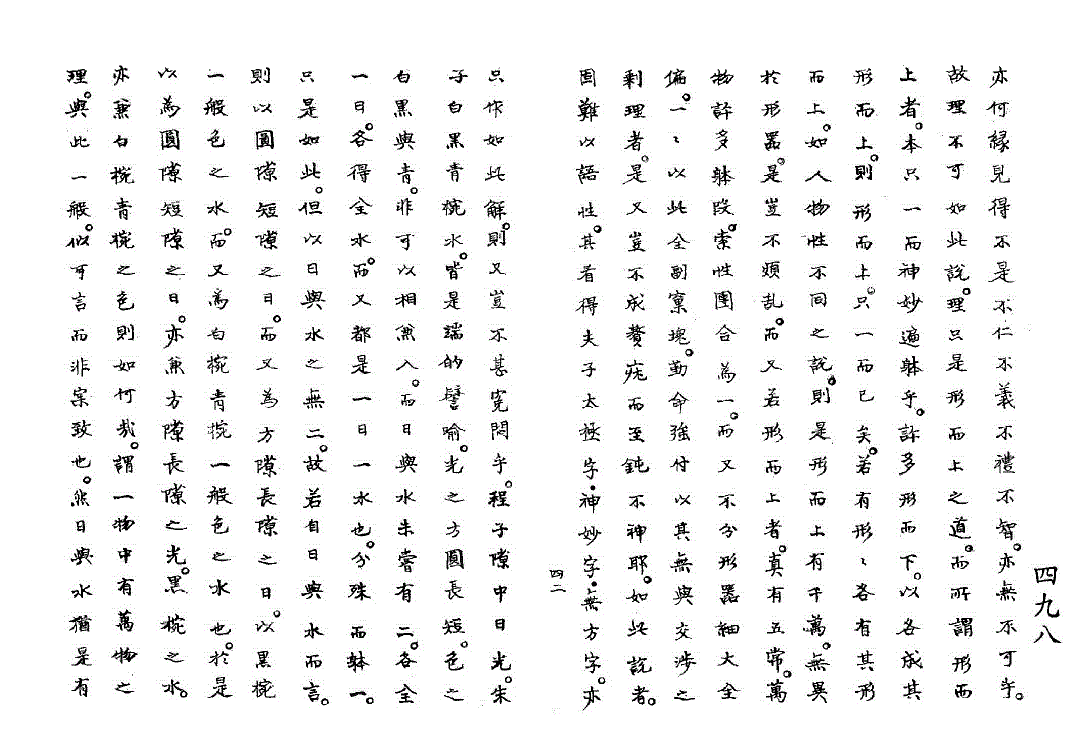 亦何缘见得不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亦无不可乎。故理不可如此说。理只是形而上之道。而所谓形而上者。本只一而神妙遍体乎。许多形而下。以各成其形而上。则形而上。只一而已矣。若有形形各有其形而上。如人物性不同之说。则是形而上有千万。无异于形器。是岂不烦乱。而又若形而上者。真有五常。万物许多体段。索性团合为一。而又不分形器细大全偏。一一以此全副窠块。勤命强付以其无与交涉之剩理者。是又岂不成赘疣而至钝不神耶。如此说者。固难以语性。其看得夫子太极字,神妙字,无方字。亦只作如此解。则又岂不甚冤闷乎。程子隙中日光。朱子白黑青碗水。皆是端的譬喻。光之方圆长短。色之白黑与青。非可以相兼入。而日与水未尝有二。各全一日。各得全水。而又都是一日一水也。分殊而体一。只是如此。但以日与水之无二。故若自日与水而言。则以圆隙短隙之日。而又为方隙长隙之日。以黑碗一般色之水。而又为白碗青碗一般色之水也。于是以为圆隙短隙之日。亦兼方隙长隙之光。黑碗之水。亦兼白碗青碗之色则如何哉。谓一物中有万物之理。与此一般。似可言而非宲致也。然日与水犹是有
亦何缘见得不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亦无不可乎。故理不可如此说。理只是形而上之道。而所谓形而上者。本只一而神妙遍体乎。许多形而下。以各成其形而上。则形而上。只一而已矣。若有形形各有其形而上。如人物性不同之说。则是形而上有千万。无异于形器。是岂不烦乱。而又若形而上者。真有五常。万物许多体段。索性团合为一。而又不分形器细大全偏。一一以此全副窠块。勤命强付以其无与交涉之剩理者。是又岂不成赘疣而至钝不神耶。如此说者。固难以语性。其看得夫子太极字,神妙字,无方字。亦只作如此解。则又岂不甚冤闷乎。程子隙中日光。朱子白黑青碗水。皆是端的譬喻。光之方圆长短。色之白黑与青。非可以相兼入。而日与水未尝有二。各全一日。各得全水。而又都是一日一水也。分殊而体一。只是如此。但以日与水之无二。故若自日与水而言。则以圆隙短隙之日。而又为方隙长隙之日。以黑碗一般色之水。而又为白碗青碗一般色之水也。于是以为圆隙短隙之日。亦兼方隙长隙之光。黑碗之水。亦兼白碗青碗之色则如何哉。谓一物中有万物之理。与此一般。似可言而非宲致也。然日与水犹是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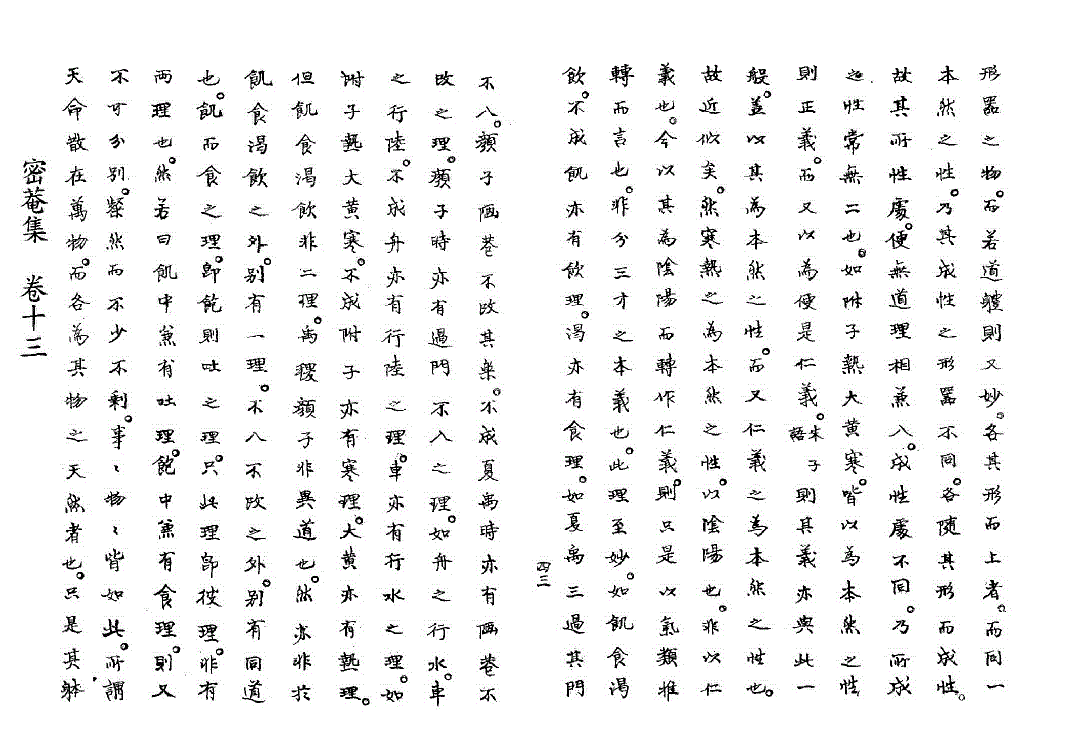 形器之物。而若道体则又妙。各其形而上者。而同一本然之性。乃其成性之形器不同。各随其形而成性。故其所性处。便无道理相兼入。成性处不同。乃所成之性常无二也。如附子热大黄寒。皆以为本然之性则正义。而又以为便是仁义。(朱子语)则其义亦与此一般。盖以其为本然之性。而又仁义之为本然之性也。故近似矣。然寒热之为本然之性。以阴阳也。非以仁义也。今以其为阴阳而转作仁义。则只是以气类推转而言也。非分三才之本义也。此理至妙。如饥食渴饮。不成饥亦有饮理。渴亦有食理。如夏禹三过其门不入。颜子陋巷不改其乐。不成夏禹时亦有陋巷不改之理。颜子时亦有过门不入之理。如舟之行水。车之行陆。不成舟亦有行陆之理。车亦有行水之理。如附子热大黄寒。不成附子亦有寒理。大黄亦有热理。但饥食渴饮非二理。禹稷颜子非异道也。然亦非于饥食渴饮之外。别有一理。不入不改之外。别有同道也。饥而食之理。即饱则吐之理。只此理即彼理。非有两理也。然若曰饥中兼有吐理。饱中兼有食理。则又不可分别。粲然而不少不剩。事事物物皆如此。所谓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然者也。只是其体
形器之物。而若道体则又妙。各其形而上者。而同一本然之性。乃其成性之形器不同。各随其形而成性。故其所性处。便无道理相兼入。成性处不同。乃所成之性常无二也。如附子热大黄寒。皆以为本然之性则正义。而又以为便是仁义。(朱子语)则其义亦与此一般。盖以其为本然之性。而又仁义之为本然之性也。故近似矣。然寒热之为本然之性。以阴阳也。非以仁义也。今以其为阴阳而转作仁义。则只是以气类推转而言也。非分三才之本义也。此理至妙。如饥食渴饮。不成饥亦有饮理。渴亦有食理。如夏禹三过其门不入。颜子陋巷不改其乐。不成夏禹时亦有陋巷不改之理。颜子时亦有过门不入之理。如舟之行水。车之行陆。不成舟亦有行陆之理。车亦有行水之理。如附子热大黄寒。不成附子亦有寒理。大黄亦有热理。但饥食渴饮非二理。禹稷颜子非异道也。然亦非于饥食渴饮之外。别有一理。不入不改之外。别有同道也。饥而食之理。即饱则吐之理。只此理即彼理。非有两理也。然若曰饥中兼有吐理。饱中兼有食理。则又不可分别。粲然而不少不剩。事事物物皆如此。所谓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然者也。只是其体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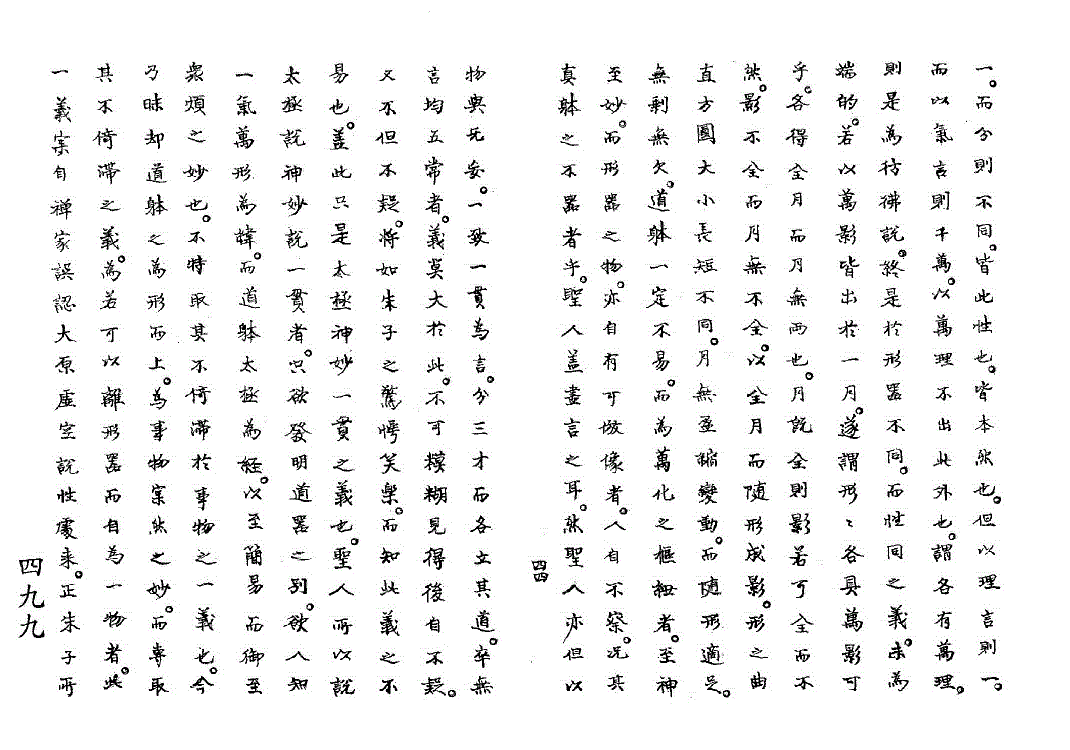 一。而分则不同。皆此性也。皆本然也。但以理言则一。而以气言则千万。以万理不出此外也。谓各有万理。则是为彷佛说。终是于形器不同。而性同之义。未为端的。若以万影皆出于一月。遂谓形形各具万影可乎。各得全月而月无两也。月既全则影若可全而不然。影不全而月无不全。以全月而随形成影。形之曲直方圆大小长短不同。月无盈缩变动。而随形适足。无剩无欠。道体一定不易。而为万化之枢纽者。至神至妙。而形器之物。亦自有可仿像者。人自不察。况其真体之不器者乎。圣人盖尽言之耳。然圣人亦但以物与无妄。一致一贯为言。分三才而各立其道。卒无言均五常者。义莫大于此。不可模糊见得后自不疑。又不但不疑。将如朱子之惊愕笑乐。而知此义之不易也。盖此只是太极神妙一贯之义也。圣人所以说太极说神妙说一贯者。只欲发明道器之别。欲人知一气万形为纬。而道体太极为经。以至简易而御至众烦之妙也。不特取其不倚滞于事物之一义也。今乃昧却道体之为形而上。为事物宲然之妙。而专取其不倚滞之义。为若可以离形器而自为一物者。此一义宲自禅家误认大原虚空说性处来。正朱子所
一。而分则不同。皆此性也。皆本然也。但以理言则一。而以气言则千万。以万理不出此外也。谓各有万理。则是为彷佛说。终是于形器不同。而性同之义。未为端的。若以万影皆出于一月。遂谓形形各具万影可乎。各得全月而月无两也。月既全则影若可全而不然。影不全而月无不全。以全月而随形成影。形之曲直方圆大小长短不同。月无盈缩变动。而随形适足。无剩无欠。道体一定不易。而为万化之枢纽者。至神至妙。而形器之物。亦自有可仿像者。人自不察。况其真体之不器者乎。圣人盖尽言之耳。然圣人亦但以物与无妄。一致一贯为言。分三才而各立其道。卒无言均五常者。义莫大于此。不可模糊见得后自不疑。又不但不疑。将如朱子之惊愕笑乐。而知此义之不易也。盖此只是太极神妙一贯之义也。圣人所以说太极说神妙说一贯者。只欲发明道器之别。欲人知一气万形为纬。而道体太极为经。以至简易而御至众烦之妙也。不特取其不倚滞于事物之一义也。今乃昧却道体之为形而上。为事物宲然之妙。而专取其不倚滞之义。为若可以离形器而自为一物者。此一义宲自禅家误认大原虚空说性处来。正朱子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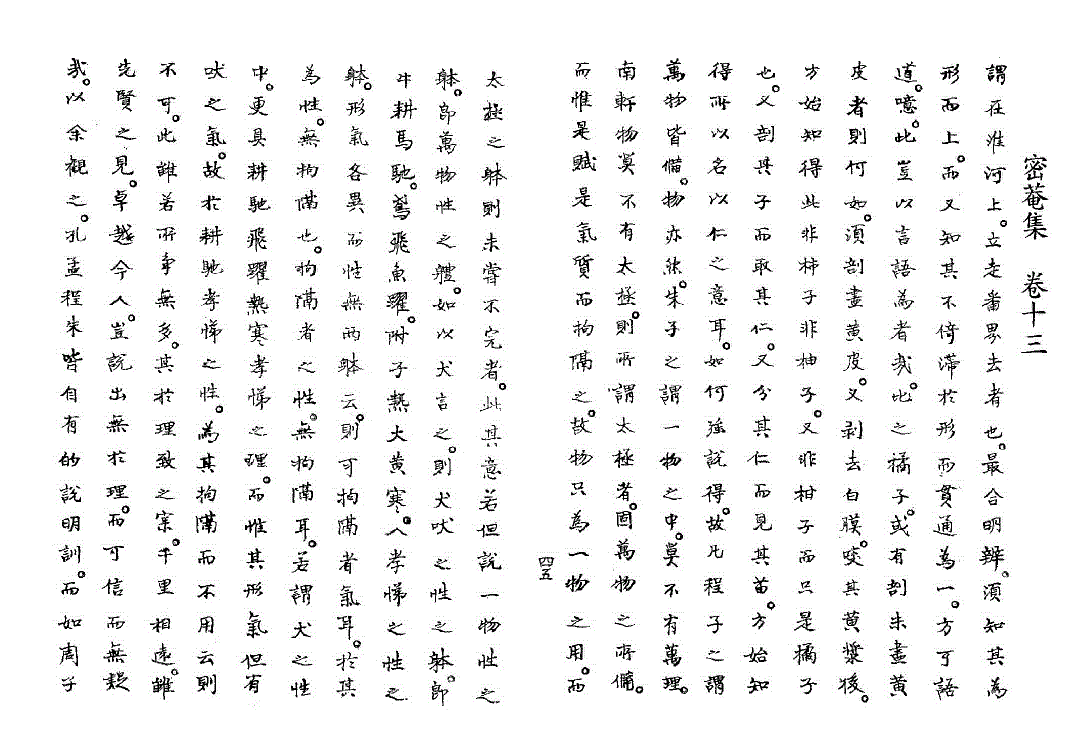 谓在淮河上。立走番界去者也。最合明辨。须知其为形而上。而又知其不倚滞于形而贯通为一。方可语道。噫。此岂以言语为者哉。比之橘子。或有剖未尽黄皮者则何如。须剖尽黄皮。又剥去白膜。啖其黄浆后。方始知得此非柿子非柚子。又非柑子而只是橘子也。又剖其子而取其仁。又分其仁而见其苗。方始知得所以名以仁之意耳。如何强说得。故凡程子之谓万物皆备。物亦然。朱子之谓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理。南轩物莫不有太极。则所谓太极者。固万物之所备。而惟是赋是气质而拘隔之。故物只为一物之用。而太极之体则未尝不完者。此其意若但说一物性之体。即万物性之体。如以犬言之。则犬吠之性之体。即牛耕马驰。鸢飞鱼跃。附子热大黄寒。人孝悌之性之体。形气各异而性无两体云。则可拘隔者气耳。于其为性。无拘隔也。拘隔者之性。无拘隔耳。若谓犬之性中。更具耕驰飞跃热寒孝悌之理。而惟其形气但有吠之气。故于耕驰孝悌之性。为其拘隔而不用云则不可。此虽若所争无多。其于理致之宲。千里相远。虽先贤之见。卓越今人。岂说出无于理。而可信而无疑哉。以余观之。孔孟程朱皆自有的说明训。而如周子
谓在淮河上。立走番界去者也。最合明辨。须知其为形而上。而又知其不倚滞于形而贯通为一。方可语道。噫。此岂以言语为者哉。比之橘子。或有剖未尽黄皮者则何如。须剖尽黄皮。又剥去白膜。啖其黄浆后。方始知得此非柿子非柚子。又非柑子而只是橘子也。又剖其子而取其仁。又分其仁而见其苗。方始知得所以名以仁之意耳。如何强说得。故凡程子之谓万物皆备。物亦然。朱子之谓一物之中。莫不有万理。南轩物莫不有太极。则所谓太极者。固万物之所备。而惟是赋是气质而拘隔之。故物只为一物之用。而太极之体则未尝不完者。此其意若但说一物性之体。即万物性之体。如以犬言之。则犬吠之性之体。即牛耕马驰。鸢飞鱼跃。附子热大黄寒。人孝悌之性之体。形气各异而性无两体云。则可拘隔者气耳。于其为性。无拘隔也。拘隔者之性。无拘隔耳。若谓犬之性中。更具耕驰飞跃热寒孝悌之理。而惟其形气但有吠之气。故于耕驰孝悌之性。为其拘隔而不用云则不可。此虽若所争无多。其于理致之宲。千里相远。虽先贤之见。卓越今人。岂说出无于理。而可信而无疑哉。以余观之。孔孟程朱皆自有的说明训。而如周子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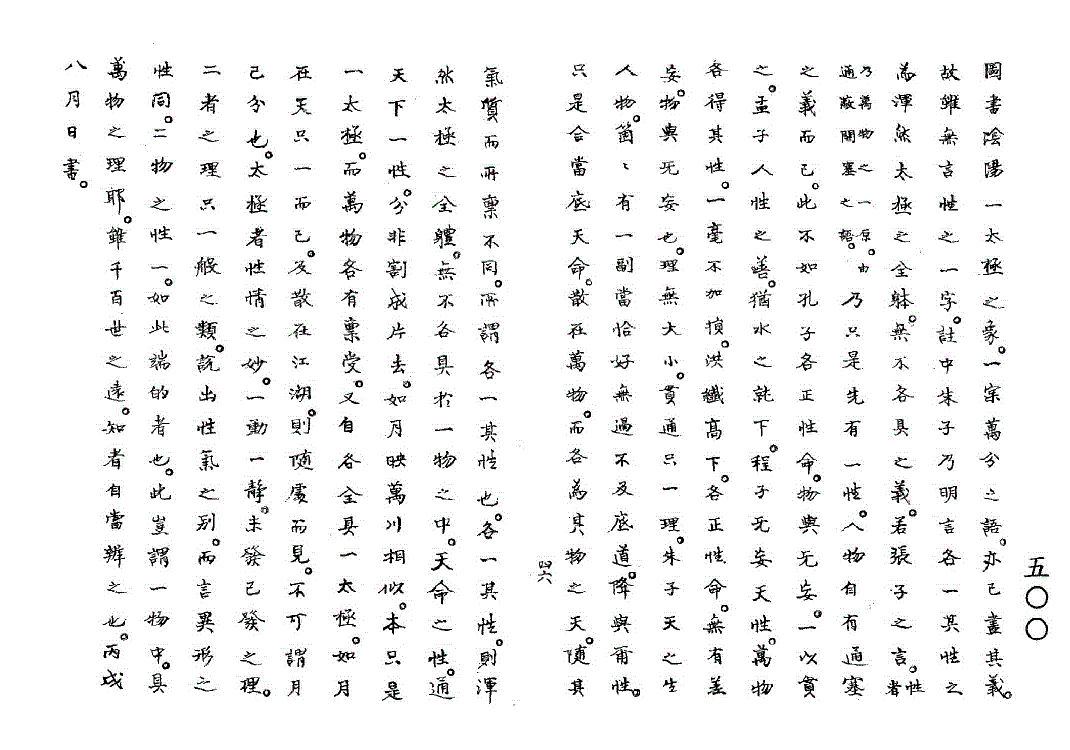 图书阴阳一太极之象。一宲万分之语。亦已尽其义。故虽无言性之一字。注中朱子乃明言各一其性之为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之义。若张子之言。(性者乃万物之一原。由通蔽开塞之语。)乃只是先有一性。人物自有通塞之义而已。此不如孔子各正性命。物与无妄。一以贯之。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程子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洪纤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理无大小。贯通只一理。朱子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降与尔性。只是合当底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分非割成片去。如月映万川相似。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太极者性情之妙。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二者之理只一般之类。说出性气之别。而言异形之性同。二物之性一。如此端的者也。此岂谓一物中。具万物之理耶。虽千百世之远。知者自当辨之也。丙戌八月日书。
图书阴阳一太极之象。一宲万分之语。亦已尽其义。故虽无言性之一字。注中朱子乃明言各一其性之为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之义。若张子之言。(性者乃万物之一原。由通蔽开塞之语。)乃只是先有一性。人物自有通塞之义而已。此不如孔子各正性命。物与无妄。一以贯之。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程子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洪纤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理无大小。贯通只一理。朱子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降与尔性。只是合当底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分非割成片去。如月映万川相似。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太极者性情之妙。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二者之理只一般之类。说出性气之别。而言异形之性同。二物之性一。如此端的者也。此岂谓一物中。具万物之理耶。虽千百世之远。知者自当辨之也。丙戌八月日书。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01H 页
 读山陵奏
读山陵奏天有寒暑阴晴和乖祥祲之异。人有刚柔清浊智愚邪正之异。地有燥湿虚实美恶安危之异。同一理也。天道有象。可推验。人为有迹。可考惩。惟地理未彰。最难究覈。然其理必然。但人之知有未及尔。今以地理之说。为茫昧难推。虽如朱子奏状。历历作真实事者。犹不之信。而反以为病者。是为上古无明教也。若知阳而不知阴。知人而不知地。知生而不知死。知明而不知幽。知神而不知鬼。知见闻所及而不知见闻所不及。则是自蔽而不知者也。非能真知物理之尽。而穷夫本末之致者也。古之不言。亦未及明也。特其未明而不言。则无伤于明而已矣。凡天下事物。古无而今有。古不言而今乃著者。何可胜数哉。其知后世乃显者。其理隐也。非无也。地理之必有则无疑。而能尽地之理者。诚不易其真知安危吉凶。则须精巧入神者可能。而精巧者不世出。人之生死者。举世安得每人而卜安吉之藏。况举天下之地。而其安且吉者无几。而人之死则无穷。果如朱子之说。穴如医者针灸。毫釐不可差。祖茔之侧。惊动挻灾。而人人各葬一山。则人众地小。理无可行。抑地之安吉者亦无穷。而犹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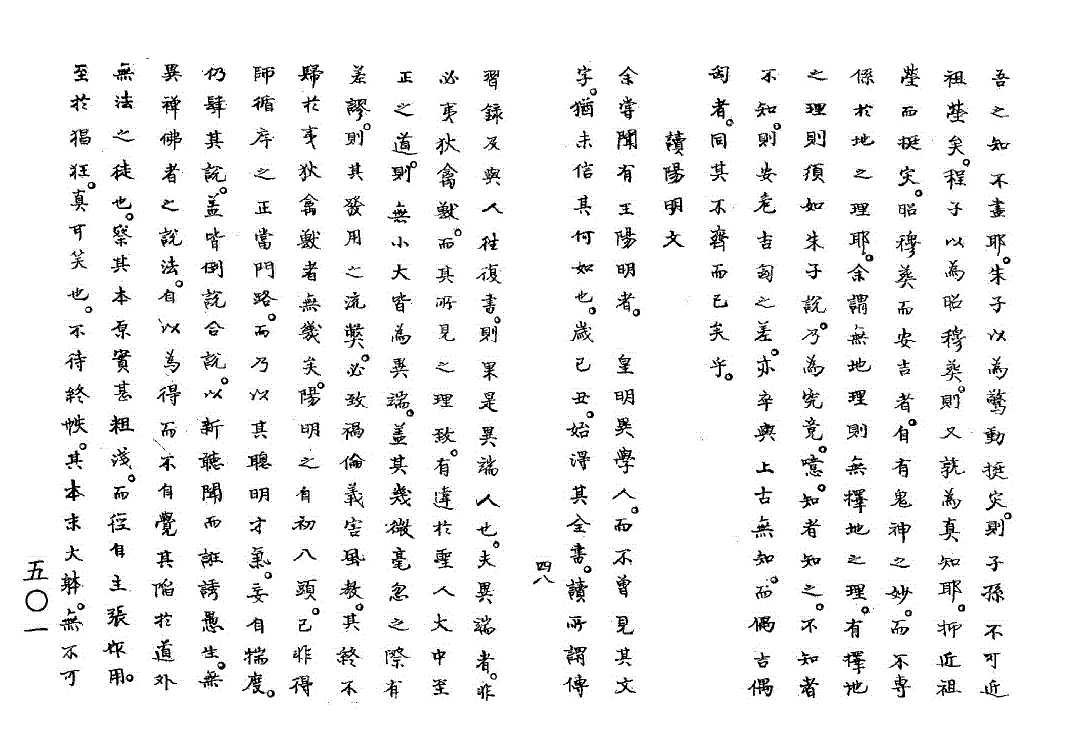 吾之知不尽耶。朱子以为惊动挺(一作挻)灾。则子孙不可近祖茔矣。程子以为昭穆葬。则又孰为真知耶。抑近祖茔而挺(一作挻)灾。昭穆葬而安吉者。自有鬼神之妙。而不专系于地之理耶。余谓无地理则无择地之理。有择地之理则须如朱子说。乃为究竟。噫。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则安危吉匈之差。亦卒与上古无知。而偶吉偶匈者。同其不齐而已矣乎。
吾之知不尽耶。朱子以为惊动挺(一作挻)灾。则子孙不可近祖茔矣。程子以为昭穆葬。则又孰为真知耶。抑近祖茔而挺(一作挻)灾。昭穆葬而安吉者。自有鬼神之妙。而不专系于地之理耶。余谓无地理则无择地之理。有择地之理则须如朱子说。乃为究竟。噫。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则安危吉匈之差。亦卒与上古无知。而偶吉偶匈者。同其不齐而已矣乎。读阳明文
余尝闻有王阳明者。 皇明异学人。而不曾见其文字。犹未信其何如也。岁己丑。始得其全书。读所谓传习录及与人往复书。则果是异端人也。夫异端者。非必夷狄禽兽。而其所见之理致。有违于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则无小大皆为异端。盖其几微毫忽之际有差谬。则其发用之流弊。必致祸伦义害风教。其终不归于夷狄禽兽者无几矣。阳明之自初入头。已非得师循序之正当门路。而乃以其聪明才气。妄自揣度。仍肆其说。盖皆倒说合说。以新听闻而诳诱愚生。无异禅佛者之说法。自以为得而不自觉其陷于道外无法之徒也。察其本原实甚粗浅。而径自主张作用。至于猖狂。真可笑也。不待终帙。其本末大体。无不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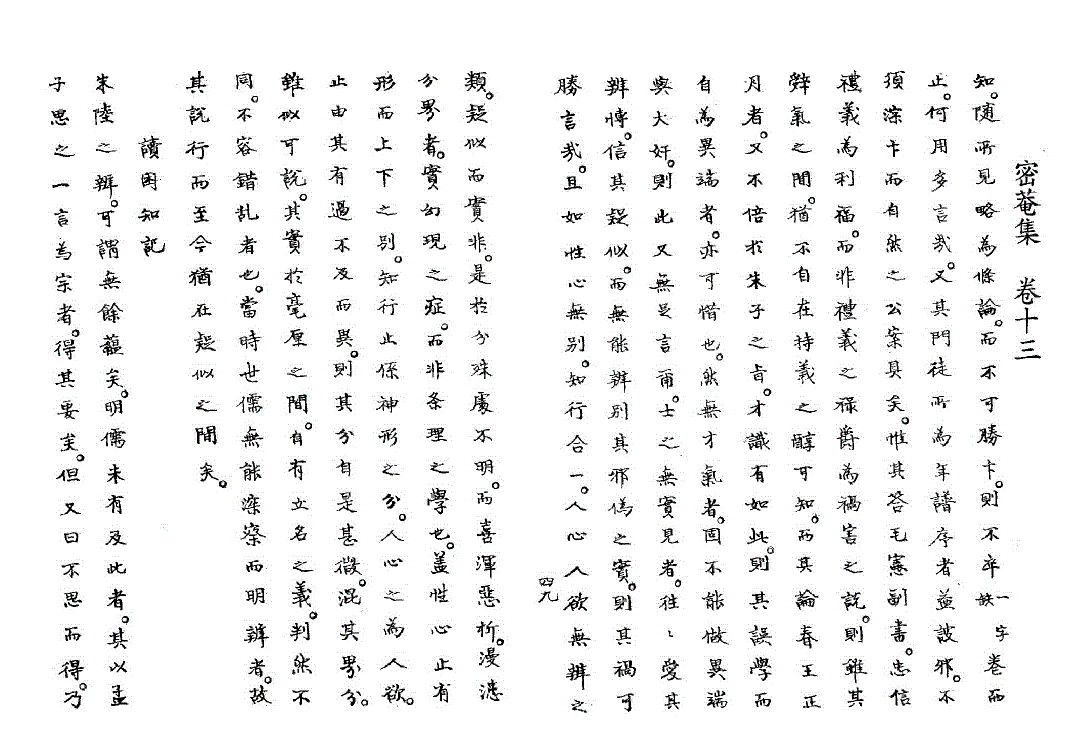 知。随所见略为条论。而不可胜卞。则不卒(一字缺)卷而止。何用多言哉。又其门徒所为年谱序者益诐邪。不须深卞而自然之公案具矣。惟其答毛宪副书。忠信礼义为利福。而非礼义之禄爵为祸害之说。则虽其辞气之间。犹不自在持义之醇可知。而其论春王正月者。又不倍于朱子之旨。才识有如此。则其误学而自为异端者。亦可惜也。然无才气者。固不能做异端与大奸。则此又无足言尔。士之无实见者。往往爱其辨博。信其疑似。而无能辨别其邪伪之实。则其祸可胜言哉。且如性心无别。知行合一。人心人欲无辨之类。疑似而实非。是于分殊处不明。而喜浑恶析。漫漶分界者。实幻现之症。而非条理之学也。盖性心止有形而上下之别。知行止系神形之分。人心之为人欲。止由其有过不及而异。则其分自是甚微。混其界分。虽似可说。其实于毫厘之间。自有立名之义。判然不同。不容错乱者也。当时世儒无能深察而明辨者。故其说行而至今犹在疑似之间矣。
知。随所见略为条论。而不可胜卞。则不卒(一字缺)卷而止。何用多言哉。又其门徒所为年谱序者益诐邪。不须深卞而自然之公案具矣。惟其答毛宪副书。忠信礼义为利福。而非礼义之禄爵为祸害之说。则虽其辞气之间。犹不自在持义之醇可知。而其论春王正月者。又不倍于朱子之旨。才识有如此。则其误学而自为异端者。亦可惜也。然无才气者。固不能做异端与大奸。则此又无足言尔。士之无实见者。往往爱其辨博。信其疑似。而无能辨别其邪伪之实。则其祸可胜言哉。且如性心无别。知行合一。人心人欲无辨之类。疑似而实非。是于分殊处不明。而喜浑恶析。漫漶分界者。实幻现之症。而非条理之学也。盖性心止有形而上下之别。知行止系神形之分。人心之为人欲。止由其有过不及而异。则其分自是甚微。混其界分。虽似可说。其实于毫厘之间。自有立名之义。判然不同。不容错乱者也。当时世儒无能深察而明辨者。故其说行而至今犹在疑似之间矣。读困知记
朱陆之辨。可谓无馀蕴矣。明儒未有及此者。其以孟子思之一言为宗者。得其要矣。但又曰不思而得。乃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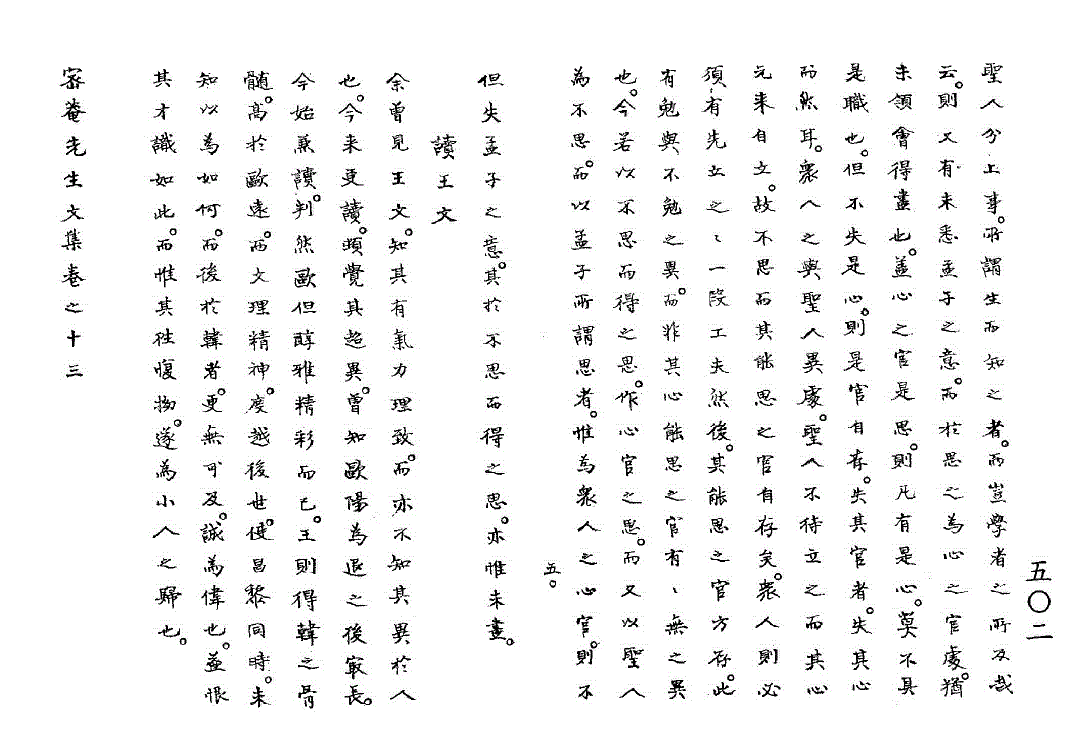 圣人分上事。所谓生而知之者。而岂学者之所及哉云。则又有未悉孟子之意。而于思之为心之官处。犹未领会得尽也。盖心之官是思。则凡有是心。莫不具是职也。但不失是心。则是官自存。失其官者。失其心而然耳。众人之与圣人异处。圣人不待立之而其心元来自立。故不思而其能思之官自存矣。众人则必须有先立之之一段工夫然后。其能思之官方存。此有勉与不勉之异。而非其心能思之官有有无之异也。今若以不思而得之思。作心官之思。而又以圣人为不思。而以孟子所谓思者。惟为众人之心官。则不但失孟子之意。其于不思而得之思。亦惟未尽。
圣人分上事。所谓生而知之者。而岂学者之所及哉云。则又有未悉孟子之意。而于思之为心之官处。犹未领会得尽也。盖心之官是思。则凡有是心。莫不具是职也。但不失是心。则是官自存。失其官者。失其心而然耳。众人之与圣人异处。圣人不待立之而其心元来自立。故不思而其能思之官自存矣。众人则必须有先立之之一段工夫然后。其能思之官方存。此有勉与不勉之异。而非其心能思之官有有无之异也。今若以不思而得之思。作心官之思。而又以圣人为不思。而以孟子所谓思者。惟为众人之心官。则不但失孟子之意。其于不思而得之思。亦惟未尽。读王文
余曾见王文。知其有气力理致。而亦不知其异于人也。今来更读。顿觉其超异。曾知欧阳为退之后最长。今始兼读。判然欧但醇雅精彩而已。王则得韩之骨髓。高于欧远。而文理精神。度越后世。使昌黎同时。未知以为如何。而后于韩者。更无可及。诚为伟也。益恨其才识如此。而惟其往愎拗。遂为小人之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