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斋集卷之六 第 x 页
定斋集卷之六
疏(七)
疏(七)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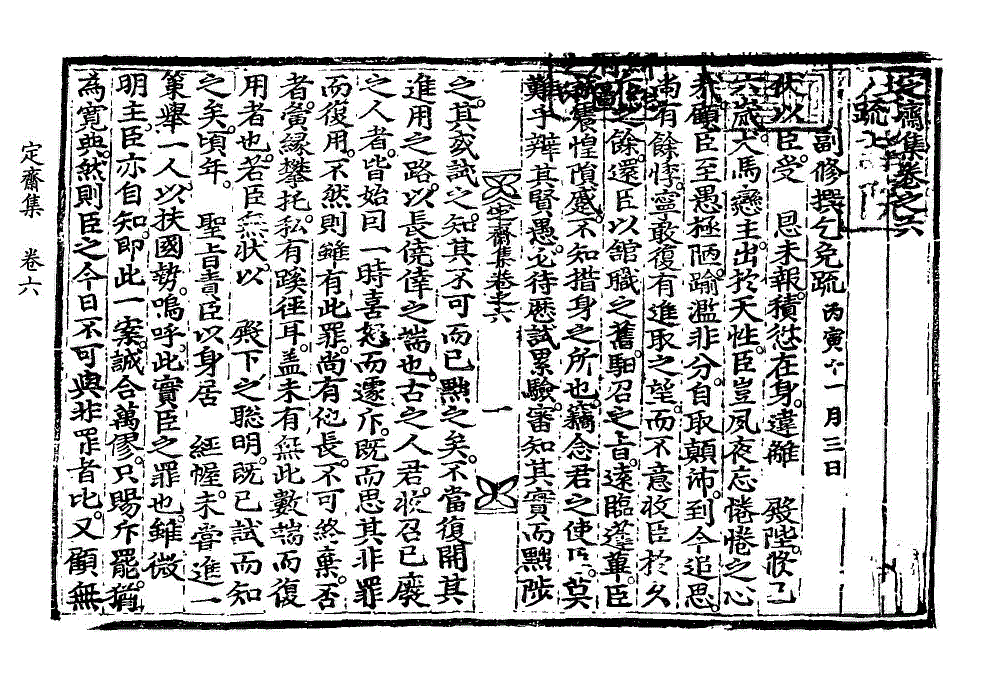 副修撰乞免疏(丙寅十一月三日)
副修撰乞免疏(丙寅十一月三日)伏以臣。受 恩未报。积愆在身。违离 殿陛。倏已六岁。犬马恋主。出于天性。臣岂夙夜忘惓惓之心哉。顾臣至愚极陋。踰滥非分。自取颠沛。到今追思。尚有馀悸。宁敢复有进取之望。而不意收臣于久斥之馀。还臣以馆职之旧。驲召之旨。远临蓬荜。臣诚震惶陨蹙。不知措身之所也。窃念君之使臣。莫难乎辨其贤愚。必待历试累验。审知其实而黜陟之。其或试之。知其不可而已黜之矣。不当复开其进用之路。以长侥倖之端也。古之人君。收召已废之人者。皆始因一时喜怒而遽斥。既而思其非罪而复用。不然则虽有此罪。尚有他长。不可终弃。否者。夤缘攀托。私有蹊径耳。盖未有无此数端而复用者也。若臣无状。以 殿下之聪明。既已试而知之矣。顷年。 圣旨责臣以身居 经幄。未尝进一策举一人。以扶国势。呜呼。此实臣之罪也。虽微 明主。臣亦自知。即此一案。诚合万僇。只赐斥罢。犹为宽典。然则臣之今日不可与非罪者比。又顾无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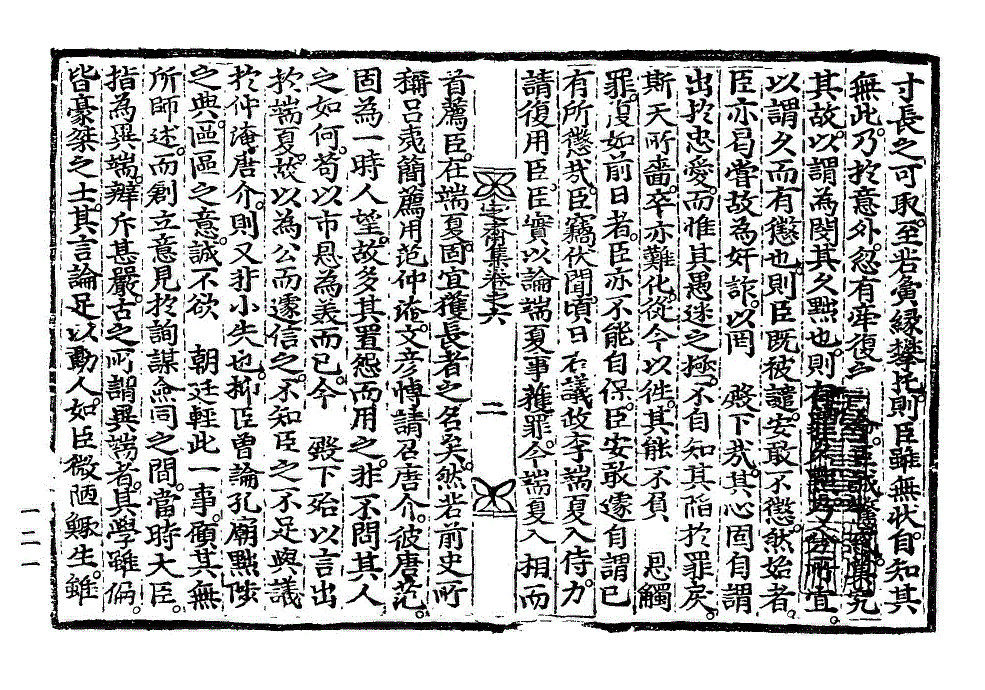 寸长之可取。至若夤缘攀托。则臣虽无状。自知其无此。乃于意外。忽有牵复之 命。臣诚惊惑。莫究其故。以谓为闵其久黜也。则有罪久黜。乃分所宜。以谓久而有惩也。则臣既被谴。安敢不惩。然始者。臣亦曷尝故为奸诈。以罔 殿下哉。其心固自谓出于忠爱。而惟其愚迷之极。不自知其陷于罪戾。斯天所啬。卒亦难化。从今以往。其能不负 恩触罪。复如前日者。臣亦不能自保。臣安敢遽自谓已有所惩哉。臣窃伏闻。顷日右议政李端夏入侍。力请复用臣。臣实以论端夏事获罪。今端夏入相而首荐臣。在端夏。固宜获长者之名矣。然若前史所称吕夷简荐用范仲淹。文彦博请召唐介。彼唐,范。固为一时人望。故多其置怨而用之。非不问其人之如何。苟以韨恩为美而已。今 殿下殆以言出于端夏。故以为公而遽信之。不知臣之不足与议于仲淹,唐介。则又非小失也。抑臣曾论孔庙黜陟之典。区区之意。诚不欲 朝廷轻此一事。顾其无所师述。而创立意见于询谋佥同之间。当时大臣。指为异端。辨斥甚严。古之所谓异端者。其学虽偏。皆豪桀之士。其言论足以动人。如臣微陋鲰生。虽
寸长之可取。至若夤缘攀托。则臣虽无状。自知其无此。乃于意外。忽有牵复之 命。臣诚惊惑。莫究其故。以谓为闵其久黜也。则有罪久黜。乃分所宜。以谓久而有惩也。则臣既被谴。安敢不惩。然始者。臣亦曷尝故为奸诈。以罔 殿下哉。其心固自谓出于忠爱。而惟其愚迷之极。不自知其陷于罪戾。斯天所啬。卒亦难化。从今以往。其能不负 恩触罪。复如前日者。臣亦不能自保。臣安敢遽自谓已有所惩哉。臣窃伏闻。顷日右议政李端夏入侍。力请复用臣。臣实以论端夏事获罪。今端夏入相而首荐臣。在端夏。固宜获长者之名矣。然若前史所称吕夷简荐用范仲淹。文彦博请召唐介。彼唐,范。固为一时人望。故多其置怨而用之。非不问其人之如何。苟以韨恩为美而已。今 殿下殆以言出于端夏。故以为公而遽信之。不知臣之不足与议于仲淹,唐介。则又非小失也。抑臣曾论孔庙黜陟之典。区区之意。诚不欲 朝廷轻此一事。顾其无所师述。而创立意见于询谋佥同之间。当时大臣。指为异端。辨斥甚严。古之所谓异端者。其学虽偏。皆豪桀之士。其言论足以动人。如臣微陋鲰生。虽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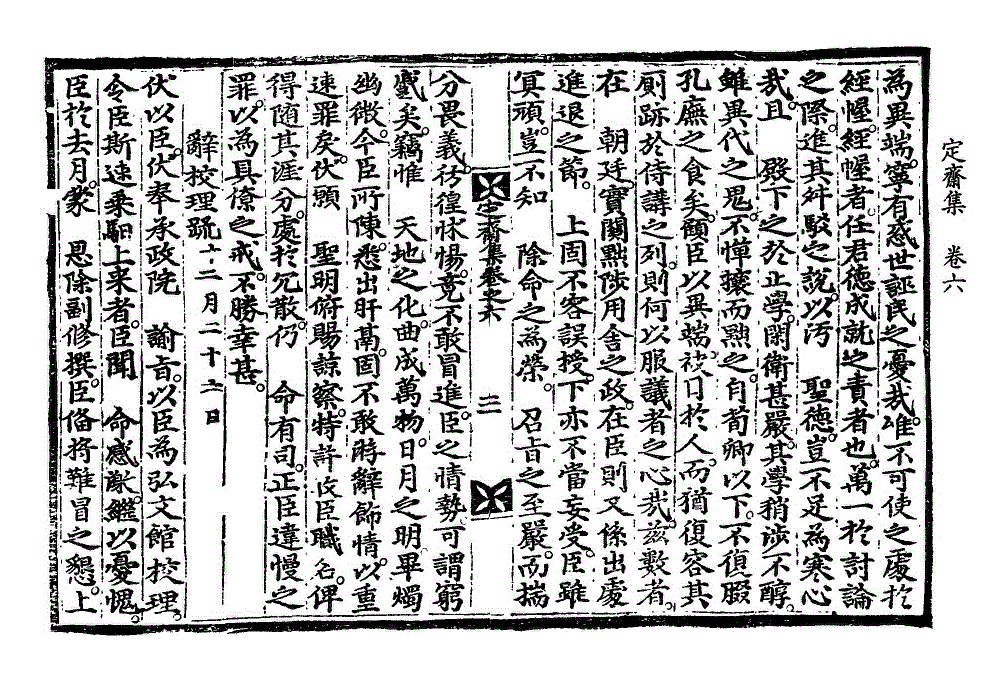 为异端。宁有惑世诬民之忧哉。唯不可使之处于经幄。经幄者。任君德成就之责者也。万一于讨论之际。进其舛驳之说。以污 圣德。岂不足为寒心哉。且 殿下之于正学。闲卫甚严。其学稍涉不醇。虽异代之鬼。不惮攘而黜之。自荀卿以下。不复啜孔庑之食矣。顾臣以异端。被日于人。而犹复容其厕迹于侍讲之列。则何以服议者之心哉。玆数者。在 朝廷。实关黜陟用舍之政。在臣则又系出处进退之节。 上固不容误授。下亦不当妄受。臣虽冥顽。岂不知 除命之为荣。 召旨之至严。而揣分畏义。彷徨怵惕。竟不敢冒进。臣之情势。可谓穷蹙矣。窃惟 天地之化。曲成万物。日月之明。毕烛幽微。今臣所陈。悉出肝鬲。固不敢游辞饰情。以重速罪戾。伏愿 圣明俯赐谅察。特许收臣职名。俾得随其涯分。处于冗散。仍 命有司。正臣违慢之罪。以为具僚之戒。不胜幸甚。
为异端。宁有惑世诬民之忧哉。唯不可使之处于经幄。经幄者。任君德成就之责者也。万一于讨论之际。进其舛驳之说。以污 圣德。岂不足为寒心哉。且 殿下之于正学。闲卫甚严。其学稍涉不醇。虽异代之鬼。不惮攘而黜之。自荀卿以下。不复啜孔庑之食矣。顾臣以异端。被日于人。而犹复容其厕迹于侍讲之列。则何以服议者之心哉。玆数者。在 朝廷。实关黜陟用舍之政。在臣则又系出处进退之节。 上固不容误授。下亦不当妄受。臣虽冥顽。岂不知 除命之为荣。 召旨之至严。而揣分畏义。彷徨怵惕。竟不敢冒进。臣之情势。可谓穷蹙矣。窃惟 天地之化。曲成万物。日月之明。毕烛幽微。今臣所陈。悉出肝鬲。固不敢游辞饰情。以重速罪戾。伏愿 圣明俯赐谅察。特许收臣职名。俾得随其涯分。处于冗散。仍 命有司。正臣违慢之罪。以为具僚之戒。不胜幸甚。辞校理疏(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以臣。伏奉承政院 谕旨。以臣为弘文馆校理。令臣斯速乘驲上来者。臣闻 命感激。继以忧愧。臣于去月。蒙 恩除副修撰。臣备将难冒之恳。上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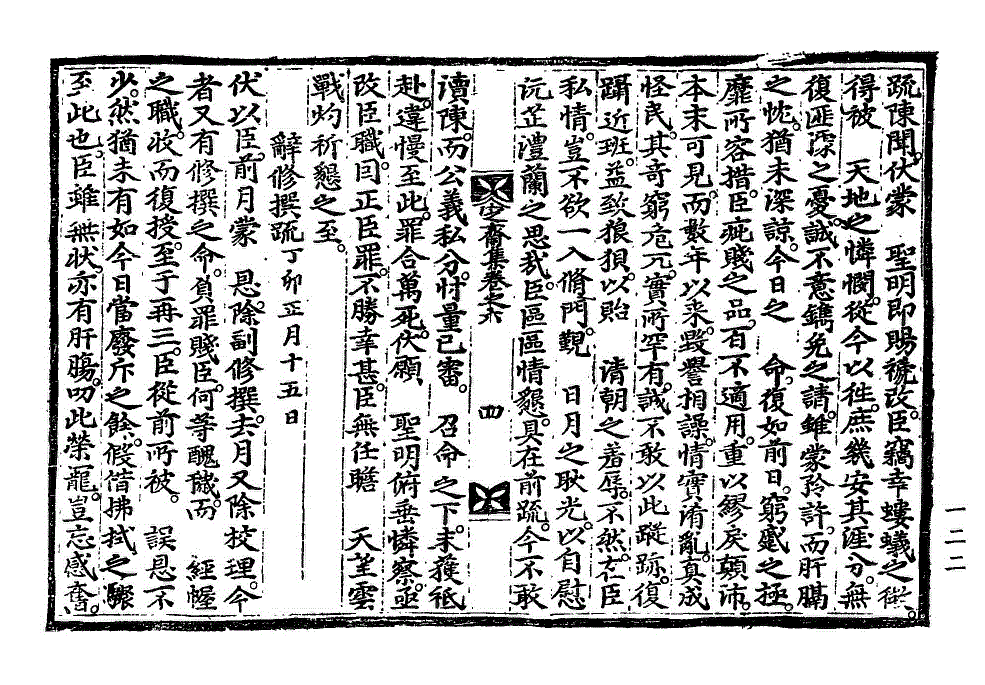 疏陈闻。伏蒙 圣明即赐褫改。臣窃幸蝼蚁之微。得被 天地之怜悯。从今以往。庶几安其涯分。无复匪据之忧。诚不意镌(一作鑴)免之请。虽蒙矜许。而肝膈之忱。犹未深谅。今日之 命。复如前日。穷蹙之极。靡所容措。臣疵贱之品。百不适用。重以缪戾颠沛。本末可见。而数年以来。毁誉相噪。情实淆乱。真成怪民。其奇穷危兀。实所罕有。诚不敢以此踪迹。复蹑近班。益致狼狈。以贻 清朝之羞辱。不然。在臣私情。岂不欲一入脩门。觐 日月之耿光。以自慰沅芷澧兰之思哉。臣区区情恳。具在前疏。今不敢渎陈。而公义私分。忖量已审。 召命之下。未获祗赴。违慢至此。罪合万死。伏愿 圣明俯垂怜察。亟改臣职。因正臣罪。不胜幸甚。臣无任瞻 天望云战灼祈恳之至。
疏陈闻。伏蒙 圣明即赐褫改。臣窃幸蝼蚁之微。得被 天地之怜悯。从今以往。庶几安其涯分。无复匪据之忧。诚不意镌(一作鑴)免之请。虽蒙矜许。而肝膈之忱。犹未深谅。今日之 命。复如前日。穷蹙之极。靡所容措。臣疵贱之品。百不适用。重以缪戾颠沛。本末可见。而数年以来。毁誉相噪。情实淆乱。真成怪民。其奇穷危兀。实所罕有。诚不敢以此踪迹。复蹑近班。益致狼狈。以贻 清朝之羞辱。不然。在臣私情。岂不欲一入脩门。觐 日月之耿光。以自慰沅芷澧兰之思哉。臣区区情恳。具在前疏。今不敢渎陈。而公义私分。忖量已审。 召命之下。未获祗赴。违慢至此。罪合万死。伏愿 圣明俯垂怜察。亟改臣职。因正臣罪。不胜幸甚。臣无任瞻 天望云战灼祈恳之至。辞修撰疏(丁卯正月十五日)
伏以臣。前月蒙 恩。除副修撰。去月又除校理。今者又有修撰之命。负罪贱臣。何等丑秽。而 经幄之职。收而复授。至于再三。臣从前所被。 误恩不少。然犹未有如今日当废斥之馀。假借拂拭之骤至此也。臣虽无状。亦有肝肠。叨此荣宠。岂忘感奋。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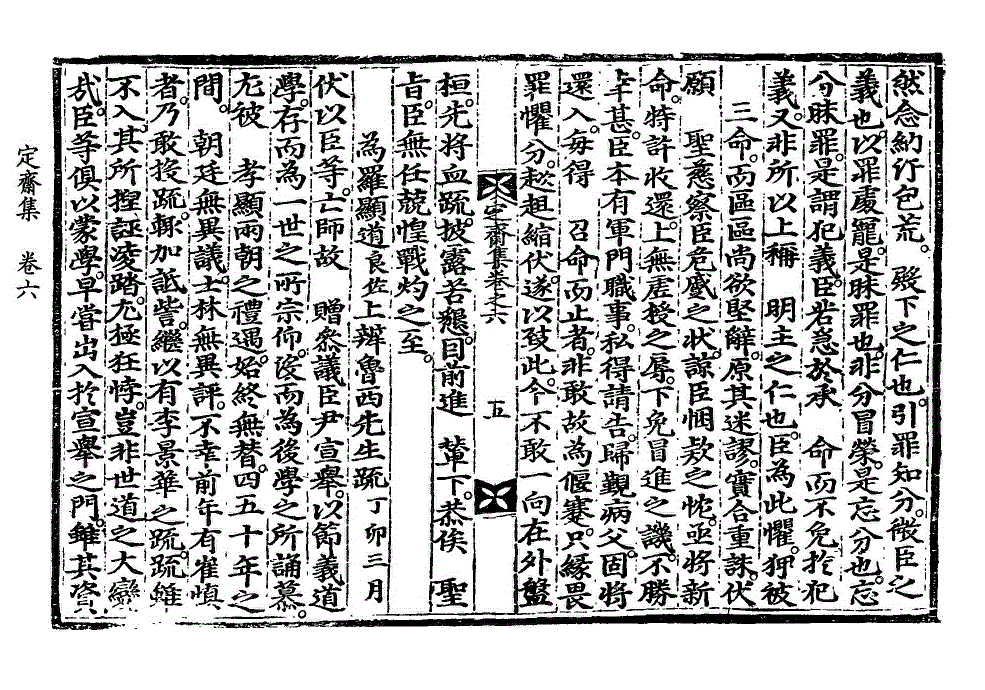 然念纳污包荒。 殿下之仁也。引罪知分。微臣之义也。以罪处宠。是昧罪也。非分冒荣。是忘分也。忘分昧罪。是谓犯义。臣若急于承 命而不免于犯义。又非所以上称 明主之仁也。臣为此惧。狎被 三命。而区区尚欲坚辞。原其迷谬。实合重诛。伏愿 圣慈察臣危蹙之状。谅臣悃款之忱。亟将新命。特许收还。上无虚授之辱。下免冒进之讥。不胜幸甚。臣本有军门职事。私得请告。归觐病父。固将还入。每得 召命而止者。非敢故为偃蹇。只缘畏罪惧分。趑趄缩伏。遂以致此。今不敢一向在外盘桓。先将血疏。披露苦恳。因前进 辇下。恭俟 圣旨。臣无任兢惶战灼之至。
然念纳污包荒。 殿下之仁也。引罪知分。微臣之义也。以罪处宠。是昧罪也。非分冒荣。是忘分也。忘分昧罪。是谓犯义。臣若急于承 命而不免于犯义。又非所以上称 明主之仁也。臣为此惧。狎被 三命。而区区尚欲坚辞。原其迷谬。实合重诛。伏愿 圣慈察臣危蹙之状。谅臣悃款之忱。亟将新命。特许收还。上无虚授之辱。下免冒进之讥。不胜幸甚。臣本有军门职事。私得请告。归觐病父。固将还入。每得 召命而止者。非敢故为偃蹇。只缘畏罪惧分。趑趄缩伏。遂以致此。今不敢一向在外盘桓。先将血疏。披露苦恳。因前进 辇下。恭俟 圣旨。臣无任兢惶战灼之至。为罗显道(良佐)上辨鲁西先生疏(丁卯三月)
伏以臣等。亡师故 赠参议臣尹宣举。以节义道学。存而为一世之所宗仰。没而为后学之所诵慕。尤被 孝显两朝之礼遇。始终无替。四五十年之间。 朝廷无异议。士林无异评。不幸前年有崔慎者。乃敢投疏。辄加诋訾。继以有李景华之疏。疏虽不入。其所捏诬凌踏。尤极狂悖。岂非世道之大变哉。臣等俱以蒙学。早尝出入于宣举之门。虽其资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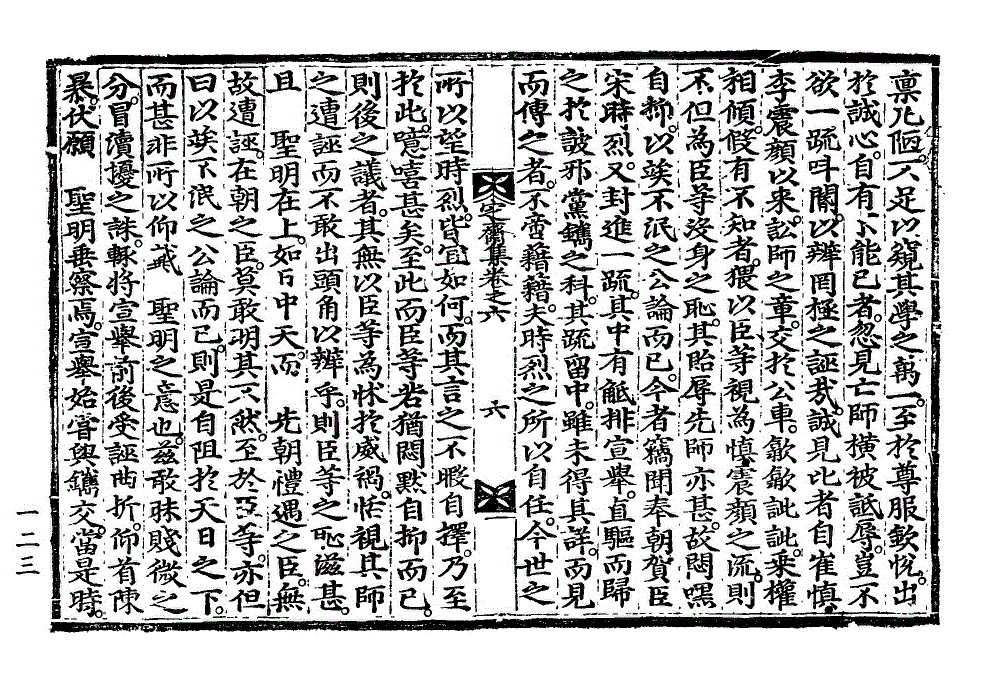 禀凡陋。不足以窥其学之万一。至于尊服钦悦。出于诚心。自有不能已者。忽见亡师横被诋辱。岂不欲一疏叫阍。以辨罔极之诬哉。诚见比者自崔慎,李震颜以来。讼师之章。交于公车。歙歙訾訾。乘权相倾。假有不知者。猥以臣等视为慎,震颜之流。则不但为臣等没身之耻。其贻辱先师亦甚。故闷嘿自抑。以俟不泯之公论而已。今者窃闻奉朝贺臣宋时烈。又封进一疏。其中有抵排宣举。直驱而归之于诐邪党镌(一作鑴)之科。其疏留中。虽未得其详。而见而传之者。不啻藉藉。夫时烈之所以自任。今世之所以望时烈。皆宜如何。而其言之不暇自择。乃至于此。噫嘻甚矣。至此而臣等若犹闷默自抑而已。则后之议者。其无以臣等为怵于威祸。恬视其师之遭诬而不敢出头角以辨乎。则臣等之耻滋甚。且 圣明在上。如日中天。而 先朝礼遇之臣。无故遭诬。在朝之臣。莫敢明其不然。至于臣等。亦但曰以俟不泯之公论而已。则是自阻于天日之下。而甚非所以仰戴 圣明之意也。玆敢昧贱微之分。冒渎扰之诛。辄将宣举前后受诬曲折。仰首陈暴。伏愿 圣明垂察焉。宣举始尝与镌(一作鑴)交。当是时。
禀凡陋。不足以窥其学之万一。至于尊服钦悦。出于诚心。自有不能已者。忽见亡师横被诋辱。岂不欲一疏叫阍。以辨罔极之诬哉。诚见比者自崔慎,李震颜以来。讼师之章。交于公车。歙歙訾訾。乘权相倾。假有不知者。猥以臣等视为慎,震颜之流。则不但为臣等没身之耻。其贻辱先师亦甚。故闷嘿自抑。以俟不泯之公论而已。今者窃闻奉朝贺臣宋时烈。又封进一疏。其中有抵排宣举。直驱而归之于诐邪党镌(一作鑴)之科。其疏留中。虽未得其详。而见而传之者。不啻藉藉。夫时烈之所以自任。今世之所以望时烈。皆宜如何。而其言之不暇自择。乃至于此。噫嘻甚矣。至此而臣等若犹闷默自抑而已。则后之议者。其无以臣等为怵于威祸。恬视其师之遭诬而不敢出头角以辨乎。则臣等之耻滋甚。且 圣明在上。如日中天。而 先朝礼遇之臣。无故遭诬。在朝之臣。莫敢明其不然。至于臣等。亦但曰以俟不泯之公论而已。则是自阻于天日之下。而甚非所以仰戴 圣明之意也。玆敢昧贱微之分。冒渎扰之诛。辄将宣举前后受诬曲折。仰首陈暴。伏愿 圣明垂察焉。宣举始尝与镌(一作鑴)交。当是时。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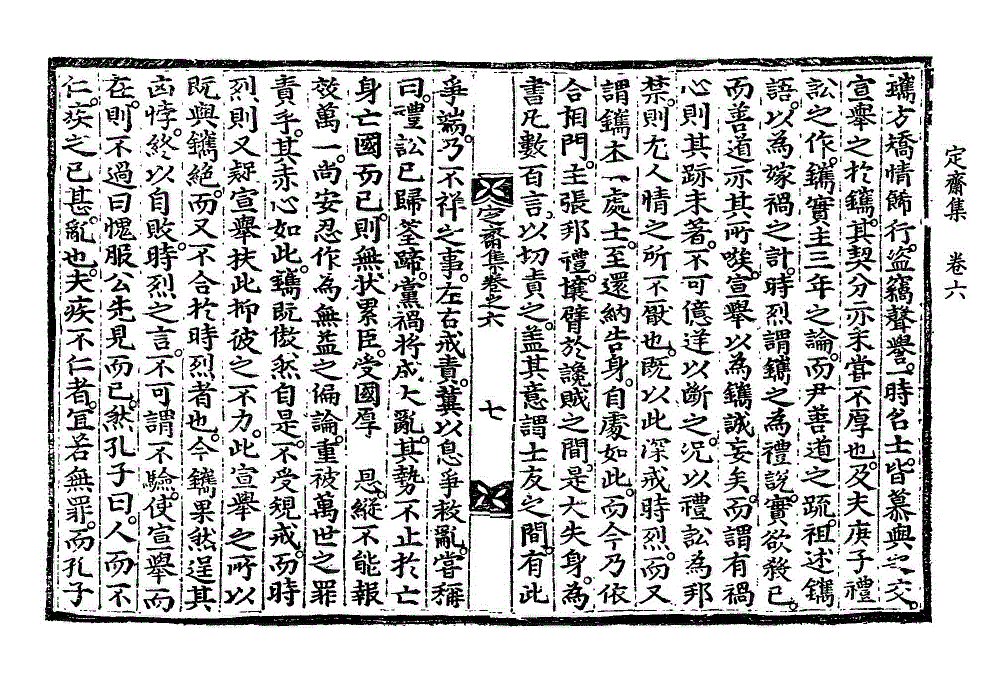 镌(一作鑴)方矫情饰行。盗窃声誉。一时名士。皆慕与之交。宣举之于镌(一作鑴)。其契分亦未尝不厚也。及夫庚子礼讼之作。镌(一作鑴)实主三年之论。而尹善道之疏。祖述镌(一作鑴)语。以为嫁祸之计。时烈谓镌(一作鑴)之为礼说。实欲杀己。而善道亦其所嗾。宣举以为镌(一作鑴)诚妄矣。而谓有祸心则其迹未著。不可亿逆以断之。况以礼讼为邦禁。则尤人情之所不厌也。既以此深戒时烈。而又谓镌(一作鑴)本一处士。至还纳告身。自处如此。而今乃依合相门。主张邦礼。攘臂于谗贼之间。是大失身。为书凡数百言。以切责之。盖其意谓士友之间。有此争端。乃不祥之事。左右戒责。冀以息争救乱。尝称曰。礼讼已归筌蹄。党祸将成大乱。其势不止于亡身亡国而已。则无状累臣。受国厚 恩。纵不能报效万一。尚安忍作为无益之偏论。重被万世之罪责乎。其赤心如此。镌(一作鑴)既傲然自是。不受规戒。而时烈则又疑宣举扶此抑彼之不力。此宣举之所以既与镌(一作鑴)绝。而又不合于时烈者也。今镌(一作鑴)果然逞其凶悖。终以自败。时烈之言。不可谓不验。使宣举而在。则不过曰愧服公先见而已。然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夫疾不仁者。宜若无罪。而孔子
镌(一作鑴)方矫情饰行。盗窃声誉。一时名士。皆慕与之交。宣举之于镌(一作鑴)。其契分亦未尝不厚也。及夫庚子礼讼之作。镌(一作鑴)实主三年之论。而尹善道之疏。祖述镌(一作鑴)语。以为嫁祸之计。时烈谓镌(一作鑴)之为礼说。实欲杀己。而善道亦其所嗾。宣举以为镌(一作鑴)诚妄矣。而谓有祸心则其迹未著。不可亿逆以断之。况以礼讼为邦禁。则尤人情之所不厌也。既以此深戒时烈。而又谓镌(一作鑴)本一处士。至还纳告身。自处如此。而今乃依合相门。主张邦礼。攘臂于谗贼之间。是大失身。为书凡数百言。以切责之。盖其意谓士友之间。有此争端。乃不祥之事。左右戒责。冀以息争救乱。尝称曰。礼讼已归筌蹄。党祸将成大乱。其势不止于亡身亡国而已。则无状累臣。受国厚 恩。纵不能报效万一。尚安忍作为无益之偏论。重被万世之罪责乎。其赤心如此。镌(一作鑴)既傲然自是。不受规戒。而时烈则又疑宣举扶此抑彼之不力。此宣举之所以既与镌(一作鑴)绝。而又不合于时烈者也。今镌(一作鑴)果然逞其凶悖。终以自败。时烈之言。不可谓不验。使宣举而在。则不过曰愧服公先见而已。然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夫疾不仁者。宜若无罪。而孔子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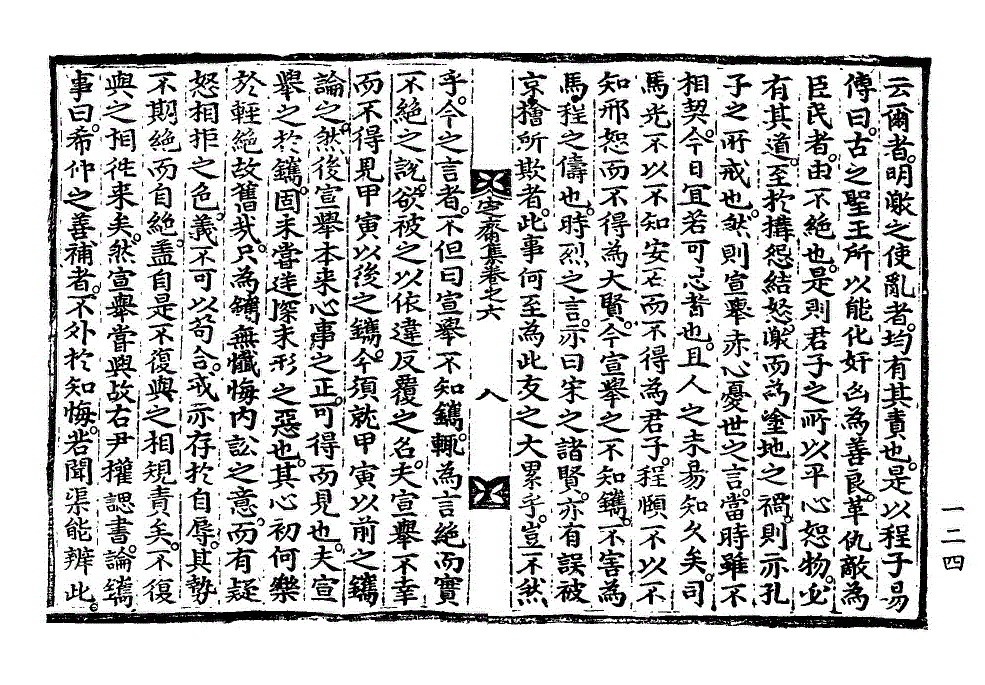 云尔者。明激之使乱者。均有其责也。是以程子易传曰。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革仇敌为臣民者。由不绝也。是则君子之所以平心恕物。必有其道。至于搆怨结怒。激而为涂地之祸。则亦孔子之所戒也。然则宣举赤心忧世之言。当时虽不相契。今日宜若可思者也。且人之未易知久矣。司马光不以不知安石而不得为君子。程颐不以不知邢恕而不得为大贤。今宣举之不知镌(一作鑴)。不害为马,程之俦也。时烈之言。亦曰宋之诸贤。亦有误被京,桧所欺者。此事何至为此友之大累乎。岂不然乎。今之言者。不但曰宣举不知镌(一作鑴)。辄为言绝而实不绝之说。欲被之以依违反覆之名。夫宣举不幸而不得见甲寅以后之镌(一作鑴)。今须就甲寅以前之镌(一作鑴)论之。然后宣举本来心事之正。可得而见也。夫宣举之于镌(一作鑴)。固未尝逆探未形之恶也。其心初何乐于轻绝故旧哉。只为镌(一作鑴)无忏悔内讼之意。而有疑怒相拒之色。义不可以苟合。戒亦存于自辱。其势不期绝而自绝。盖自是不复与之相规责矣。不复与之相往来矣。然宣举尝与故右尹权諰书。论镌(一作鑴)事曰。希仲之善补者。不外于知悔。若闻渠能辨此。
云尔者。明激之使乱者。均有其责也。是以程子易传曰。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凶为善良。革仇敌为臣民者。由不绝也。是则君子之所以平心恕物。必有其道。至于搆怨结怒。激而为涂地之祸。则亦孔子之所戒也。然则宣举赤心忧世之言。当时虽不相契。今日宜若可思者也。且人之未易知久矣。司马光不以不知安石而不得为君子。程颐不以不知邢恕而不得为大贤。今宣举之不知镌(一作鑴)。不害为马,程之俦也。时烈之言。亦曰宋之诸贤。亦有误被京,桧所欺者。此事何至为此友之大累乎。岂不然乎。今之言者。不但曰宣举不知镌(一作鑴)。辄为言绝而实不绝之说。欲被之以依违反覆之名。夫宣举不幸而不得见甲寅以后之镌(一作鑴)。今须就甲寅以前之镌(一作鑴)论之。然后宣举本来心事之正。可得而见也。夫宣举之于镌(一作鑴)。固未尝逆探未形之恶也。其心初何乐于轻绝故旧哉。只为镌(一作鑴)无忏悔内讼之意。而有疑怒相拒之色。义不可以苟合。戒亦存于自辱。其势不期绝而自绝。盖自是不复与之相规责矣。不复与之相往来矣。然宣举尝与故右尹权諰书。论镌(一作鑴)事曰。希仲之善补者。不外于知悔。若闻渠能辨此。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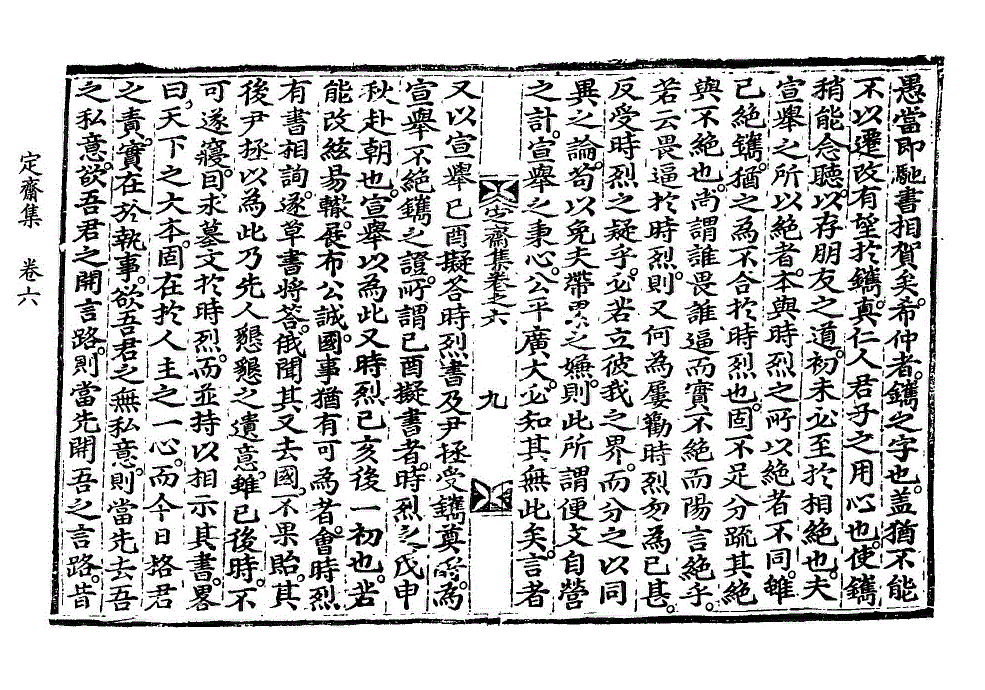 愚当即驰书相贺矣。希仲者。镌(一作鑴)之字也。盖犹不能不以迁改有望于镌(一作鑴)。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镌(一作鑴)稍能念听。以存朋友之道。初未必至于相绝也。夫宣举之所以绝者。本与时烈之所以绝者不同。虽已绝镌(一作鑴)。犹之为不合于时烈也。固不足分疏其绝与不绝也。尚谓谁畏谁逼而实不绝而阳言绝乎。若云畏逼于时烈。则又何为屡劝时烈勿为已甚。反受时烈之疑乎。必若立彼我之界。而分之以同异之论。苟以免夫带累之嫌。则此所谓便文自营之计。宣举之秉心。公平广大。必知其无此矣。言者又以宣举己酉拟答时烈书及尹拯受镌(一作鑴)奠酹。为宣举不绝镌(一作鑴)之證。所谓己酉拟书者。时烈之戊申秋赴朝也。宣举以为此又时烈己亥后一初也。若能改弦易辙。展布公诚。国事犹有可为者。会时烈有书相询。遂草书将答。俄闻其又去国。不果贻。其后尹拯以为此乃先人恳恳之遗意。虽已后时。不可遂寝。因求墓文于时烈。而并持以相示其书。略曰。天下之大本。固在于人主之一心。而今日格君之责。实在于执事。欲吾君之无私意。则当先去吾之私意。欲吾君之开言路。则当先开吾之言路。昔
愚当即驰书相贺矣。希仲者。镌(一作鑴)之字也。盖犹不能不以迁改有望于镌(一作鑴)。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镌(一作鑴)稍能念听。以存朋友之道。初未必至于相绝也。夫宣举之所以绝者。本与时烈之所以绝者不同。虽已绝镌(一作鑴)。犹之为不合于时烈也。固不足分疏其绝与不绝也。尚谓谁畏谁逼而实不绝而阳言绝乎。若云畏逼于时烈。则又何为屡劝时烈勿为已甚。反受时烈之疑乎。必若立彼我之界。而分之以同异之论。苟以免夫带累之嫌。则此所谓便文自营之计。宣举之秉心。公平广大。必知其无此矣。言者又以宣举己酉拟答时烈书及尹拯受镌(一作鑴)奠酹。为宣举不绝镌(一作鑴)之證。所谓己酉拟书者。时烈之戊申秋赴朝也。宣举以为此又时烈己亥后一初也。若能改弦易辙。展布公诚。国事犹有可为者。会时烈有书相询。遂草书将答。俄闻其又去国。不果贻。其后尹拯以为此乃先人恳恳之遗意。虽已后时。不可遂寝。因求墓文于时烈。而并持以相示其书。略曰。天下之大本。固在于人主之一心。而今日格君之责。实在于执事。欲吾君之无私意。则当先去吾之私意。欲吾君之开言路。则当先开吾之言路。昔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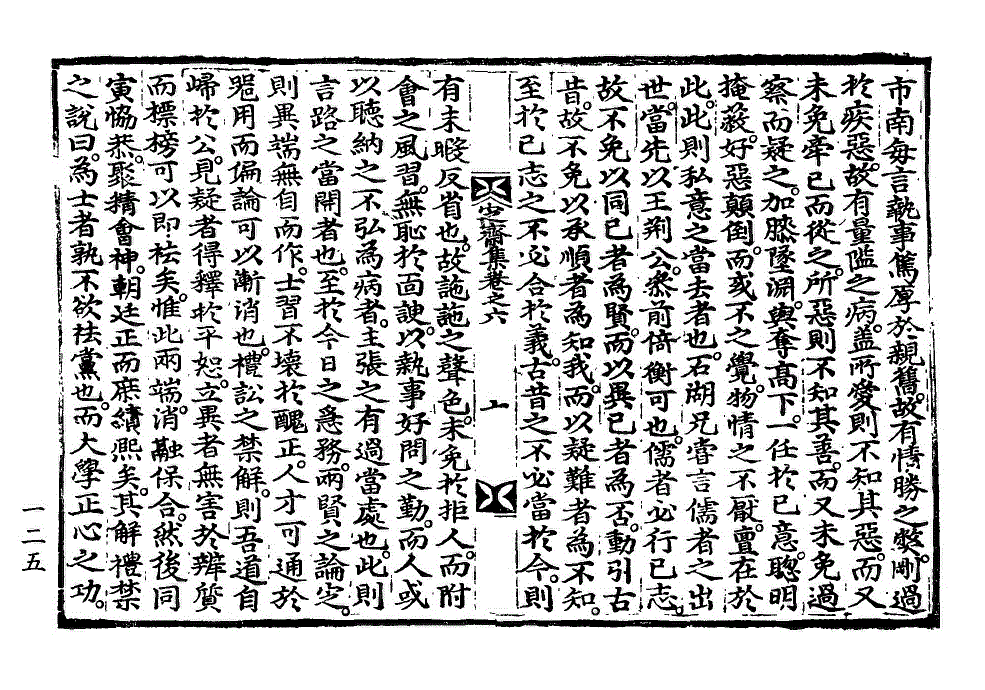 韨南每言执事笃厚于亲旧。故有情胜之弊。刚过于疾恶。故有量隘之病。盖所爱则不知其恶。而又未免牵己而从之。所恶则不知其善。而又未免过察而疑之。加膝坠渊。与夺高下。一任于己意。聪明掩蔽。好恶颠倒。而或不之觉。物情之不厌。亶在于此。此则私意之当去者也。石湖兄尝言儒者之出世。当先以王荆公。参前倚衡可也。儒者必行己志。故不免以同己者为贤。而以异己者为否。动引古昔。故不免以承顺者为知我。而以疑难者为不知。至于己志之不必合于义。古昔之不必当于今。则有未暇反省也。故訑訑之声色。未免于拒人。而附会之风习。无耻于面谀。以执事好问之勤。而人或以听纳之不弘为病者。主张之有过当处也。此则言路之当开者也。至于今日之急务。两贤之论定。则异端无自而作。士习不坏于丑正。人才可通于器用而偏论可以渐消也。礼讼之禁解。则吾道自归于公。见疑者得释于平恕。立异者无害于辨质而标榜可以即祛矣。惟此两端。消融保合。然后同寅协恭。聚精会神。朝廷正而庶绩熙矣。其解礼禁之说曰。为士者孰不欲祛党也。而大学正心之功。
韨南每言执事笃厚于亲旧。故有情胜之弊。刚过于疾恶。故有量隘之病。盖所爱则不知其恶。而又未免牵己而从之。所恶则不知其善。而又未免过察而疑之。加膝坠渊。与夺高下。一任于己意。聪明掩蔽。好恶颠倒。而或不之觉。物情之不厌。亶在于此。此则私意之当去者也。石湖兄尝言儒者之出世。当先以王荆公。参前倚衡可也。儒者必行己志。故不免以同己者为贤。而以异己者为否。动引古昔。故不免以承顺者为知我。而以疑难者为不知。至于己志之不必合于义。古昔之不必当于今。则有未暇反省也。故訑訑之声色。未免于拒人。而附会之风习。无耻于面谀。以执事好问之勤。而人或以听纳之不弘为病者。主张之有过当处也。此则言路之当开者也。至于今日之急务。两贤之论定。则异端无自而作。士习不坏于丑正。人才可通于器用而偏论可以渐消也。礼讼之禁解。则吾道自归于公。见疑者得释于平恕。立异者无害于辨质而标榜可以即祛矣。惟此两端。消融保合。然后同寅协恭。聚精会神。朝廷正而庶绩熙矣。其解礼禁之说曰。为士者孰不欲祛党也。而大学正心之功。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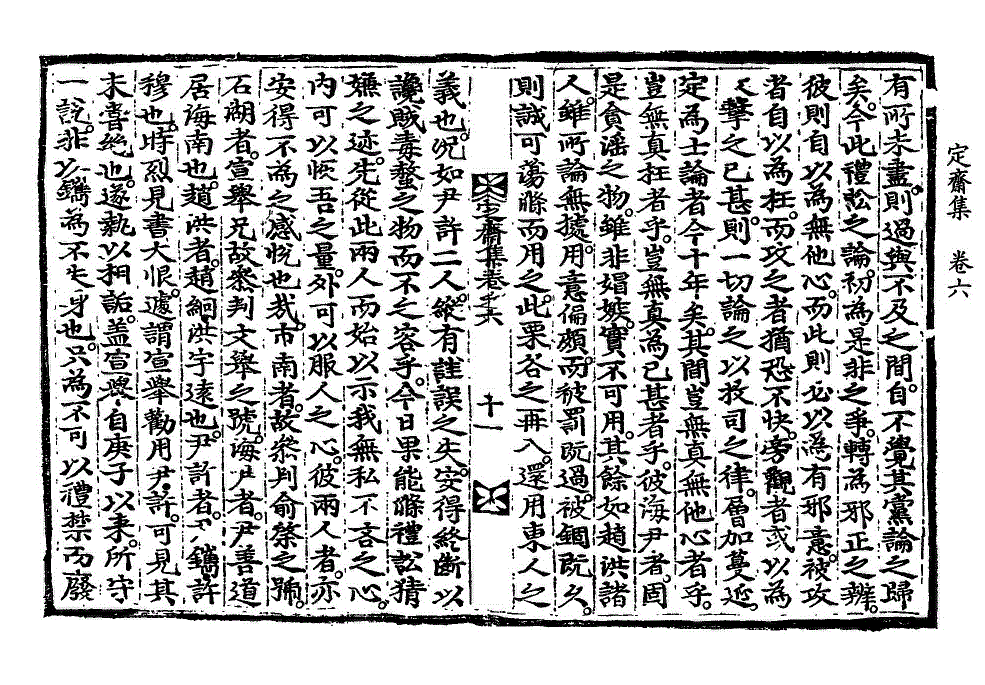 有所未尽。则过与不及之间。自不觉其党论之归矣。今此礼讼之论。初为是非之争。转为邪正之辨。彼则自以为无他心。而此则必以为有邪意。被攻者自以为枉。而攻之者犹恐不快。旁观者或以为攻击之已甚。则一切论之以收司之律。层加蔓延。定为士论者今十年矣。其间岂无真无他心者乎。岂无真枉者乎。岂无真为已甚者乎。彼海尹者。固是贪淫之物。虽非媢嫉。实不可用。其馀如赵洪诸人。虽所论无据。用意偏颇。而被罚既过。被锢既久。则诚可荡涤而用之。此栗谷之再入。还用东人之义也。况如尹许二人。纵有诖误之失。安得终断以谗贼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今日果能涤礼讼猜嫌之迹。先从此两人而始以示我无私不吝之心。内可以恢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彼两人者。亦安得不为之感悦也哉。韨南者。故参判俞棨之号。石湖者。宣举兄故参判文举之号。海尹者。尹善道居海南也。赵洪者。赵絅,洪宇远也。尹许者。尹镌(一作鑴),许穆也。时烈见书大恨。遽谓宣举劝用尹,许。可见其未尝绝也。遂执以相诟。盖宣举自庚子以来。所守一说。非以镌(一作鑴)为不失身也。只为不可以礼禁而废
有所未尽。则过与不及之间。自不觉其党论之归矣。今此礼讼之论。初为是非之争。转为邪正之辨。彼则自以为无他心。而此则必以为有邪意。被攻者自以为枉。而攻之者犹恐不快。旁观者或以为攻击之已甚。则一切论之以收司之律。层加蔓延。定为士论者今十年矣。其间岂无真无他心者乎。岂无真枉者乎。岂无真为已甚者乎。彼海尹者。固是贪淫之物。虽非媢嫉。实不可用。其馀如赵洪诸人。虽所论无据。用意偏颇。而被罚既过。被锢既久。则诚可荡涤而用之。此栗谷之再入。还用东人之义也。况如尹许二人。纵有诖误之失。安得终断以谗贼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今日果能涤礼讼猜嫌之迹。先从此两人而始以示我无私不吝之心。内可以恢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彼两人者。亦安得不为之感悦也哉。韨南者。故参判俞棨之号。石湖者。宣举兄故参判文举之号。海尹者。尹善道居海南也。赵洪者。赵絅,洪宇远也。尹许者。尹镌(一作鑴),许穆也。时烈见书大恨。遽谓宣举劝用尹,许。可见其未尝绝也。遂执以相诟。盖宣举自庚子以来。所守一说。非以镌(一作鑴)为不失身也。只为不可以礼禁而废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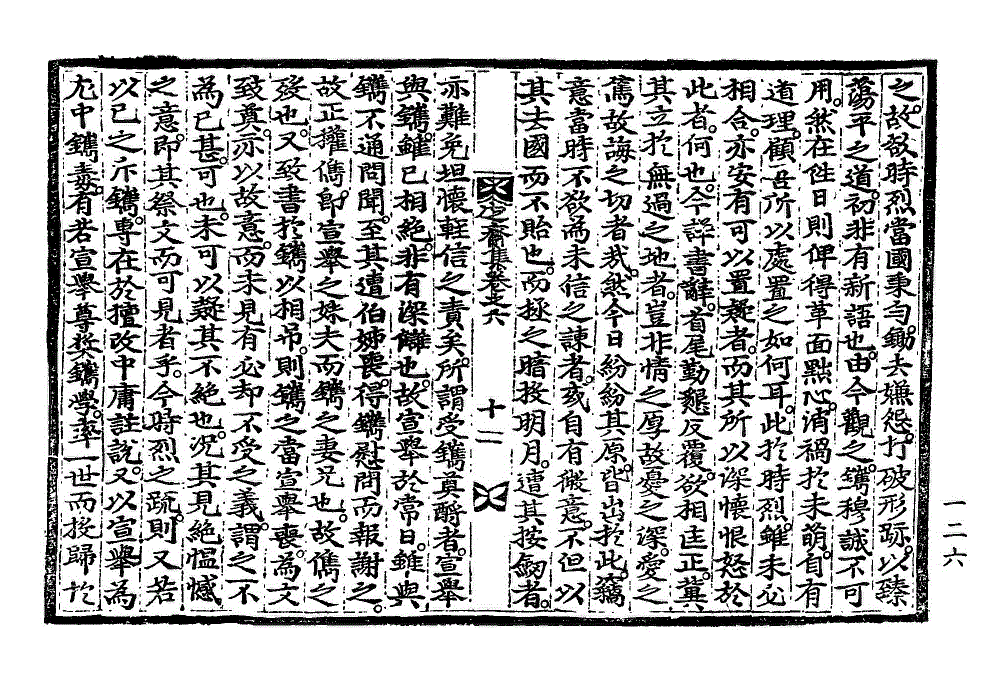 之。故欲时烈当国秉匀。锄去嫌怨。打破形迹。以臻荡平之道。初非有新语也。由今观之。镌(一作鑴)穆诚不可用。然在往日则俾得革面黜心。消祸于未萌。自有道理。顾吾所以处置之如何耳。此于时烈。虽未必相合。亦安有可以置疑者。而其所以深怀恨怒于此者。何也。今详书辞。首尾勤恳反覆。欲相匡正。冀其立于无过之地者。岂非情之厚故忧之深。爱之笃故诲之切者哉。然今日纷纷其原。皆出于此。窃意当时不欲为未信之谏者。或自有微意。不但以其去国而不贻也。而拯之暗投明月。遭其按剑者。亦难免坦怀轻信之责矣。所谓受镌(一作鑴)奠酹者。宣举与镌(一作鑴)。虽已相绝。非有深雠也。故宣举于常日。虽与镌(一作鑴)不通问闻。至其遭伯姊丧。得镌(一作鑴)慰问而报谢之。故正权俊。即宣举之妹夫而镌(一作鑴)之妻兄也。故俊之殁也。又致书于镌(一作鑴)以相吊。则镌(一作鑴)之当宣举丧。为文致奠。亦以故意。而未见有必却不受之义。谓之不为已甚。可也。未可以疑其不绝也。况其见绝愠憾之意。即其祭文而可见者乎。今时烈之疏。则又若以己之斥镌(一作鑴)。专在于擅改中庸注说。又以宣举为尤中镌(一作鑴)毒。有若宣举尊奖镌(一作鑴)学。率一世而投归于
之。故欲时烈当国秉匀。锄去嫌怨。打破形迹。以臻荡平之道。初非有新语也。由今观之。镌(一作鑴)穆诚不可用。然在往日则俾得革面黜心。消祸于未萌。自有道理。顾吾所以处置之如何耳。此于时烈。虽未必相合。亦安有可以置疑者。而其所以深怀恨怒于此者。何也。今详书辞。首尾勤恳反覆。欲相匡正。冀其立于无过之地者。岂非情之厚故忧之深。爱之笃故诲之切者哉。然今日纷纷其原。皆出于此。窃意当时不欲为未信之谏者。或自有微意。不但以其去国而不贻也。而拯之暗投明月。遭其按剑者。亦难免坦怀轻信之责矣。所谓受镌(一作鑴)奠酹者。宣举与镌(一作鑴)。虽已相绝。非有深雠也。故宣举于常日。虽与镌(一作鑴)不通问闻。至其遭伯姊丧。得镌(一作鑴)慰问而报谢之。故正权俊。即宣举之妹夫而镌(一作鑴)之妻兄也。故俊之殁也。又致书于镌(一作鑴)以相吊。则镌(一作鑴)之当宣举丧。为文致奠。亦以故意。而未见有必却不受之义。谓之不为已甚。可也。未可以疑其不绝也。况其见绝愠憾之意。即其祭文而可见者乎。今时烈之疏。则又若以己之斥镌(一作鑴)。专在于擅改中庸注说。又以宣举为尤中镌(一作鑴)毒。有若宣举尊奖镌(一作鑴)学。率一世而投归于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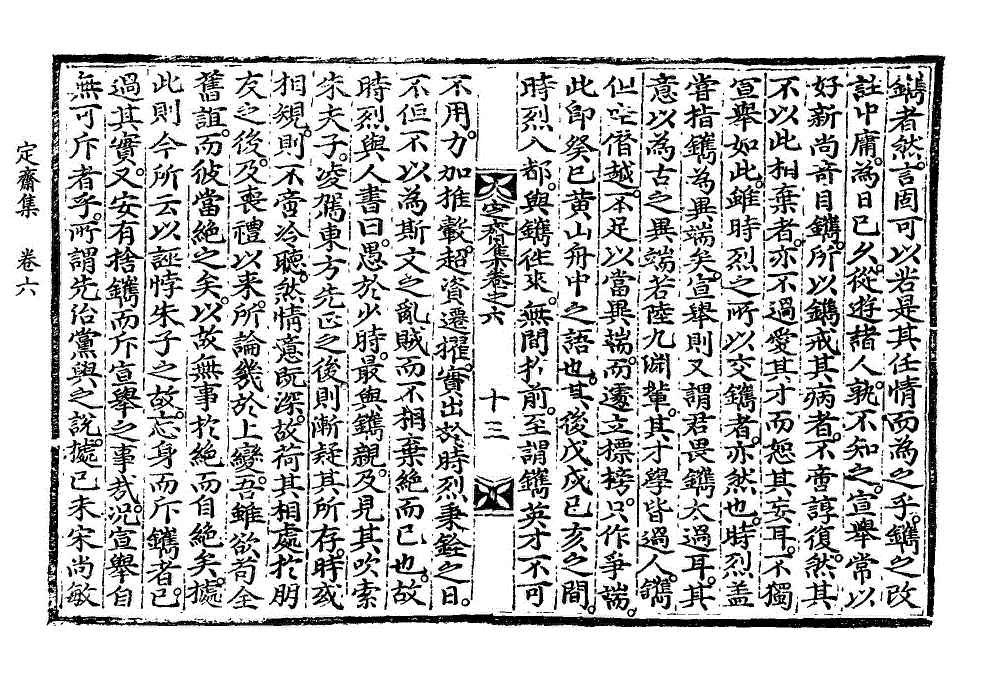 镌(一作鑴)者然。言固可以若是其任情而为之乎。镌(一作鑴)之改注中庸。为日已久。从游诸人。孰不知之。宣举常以好新尚奇目镌(一作鑴)。所以镌戒其病者。不啻谆复。然其不以此相弃者。亦不过爱其才而恕其妄耳。不独宣举如此。虽时烈之所以交镌(一作鑴)者。亦然也。时烈盖尝指镌(一作鑴)为异端矣。宣举则又谓君畏镌(一作鑴)太过耳。其意以为古之异端若陆九渊辈。其才学皆过人。镌(一作鑴)但坐僭越。不足以当异端。而遽立标榜。只作争端。此即癸巳黄山舟中之语也。其后戊戌己亥之间。时烈入都。与镌(一作鑴)往来。无间于前。至谓镌(一作鑴)英才不可不用。力加推毂。超资迁擢。实出于时烈秉铨之日。不但不以为斯文之乱贼而不相弃绝而已也。故时烈与人书曰。愚于少时。最与镌(一作鑴)亲。及见其吹索朱夫子。凌驾东方先正之后。则渐疑其所存。时或相规。则不啻冷听。然情意既深。故荷其相处于朋友之后。及丧礼以来。所论几于上变。吾虽欲苟全旧谊。而彼当绝之矣。以故无事于绝而自绝矣。据此则今所云以诬悖朱子之故。忘身而斥镌(一作鑴)者。已过其实。又安有舍镌(一作鑴)而斥宣举之事哉。况宣举自无可斥者乎。所谓先治党与之说。据己未宋尚敏
镌(一作鑴)者然。言固可以若是其任情而为之乎。镌(一作鑴)之改注中庸。为日已久。从游诸人。孰不知之。宣举常以好新尚奇目镌(一作鑴)。所以镌戒其病者。不啻谆复。然其不以此相弃者。亦不过爱其才而恕其妄耳。不独宣举如此。虽时烈之所以交镌(一作鑴)者。亦然也。时烈盖尝指镌(一作鑴)为异端矣。宣举则又谓君畏镌(一作鑴)太过耳。其意以为古之异端若陆九渊辈。其才学皆过人。镌(一作鑴)但坐僭越。不足以当异端。而遽立标榜。只作争端。此即癸巳黄山舟中之语也。其后戊戌己亥之间。时烈入都。与镌(一作鑴)往来。无间于前。至谓镌(一作鑴)英才不可不用。力加推毂。超资迁擢。实出于时烈秉铨之日。不但不以为斯文之乱贼而不相弃绝而已也。故时烈与人书曰。愚于少时。最与镌(一作鑴)亲。及见其吹索朱夫子。凌驾东方先正之后。则渐疑其所存。时或相规。则不啻冷听。然情意既深。故荷其相处于朋友之后。及丧礼以来。所论几于上变。吾虽欲苟全旧谊。而彼当绝之矣。以故无事于绝而自绝矣。据此则今所云以诬悖朱子之故。忘身而斥镌(一作鑴)者。已过其实。又安有舍镌(一作鑴)而斥宣举之事哉。况宣举自无可斥者乎。所谓先治党与之说。据己未宋尚敏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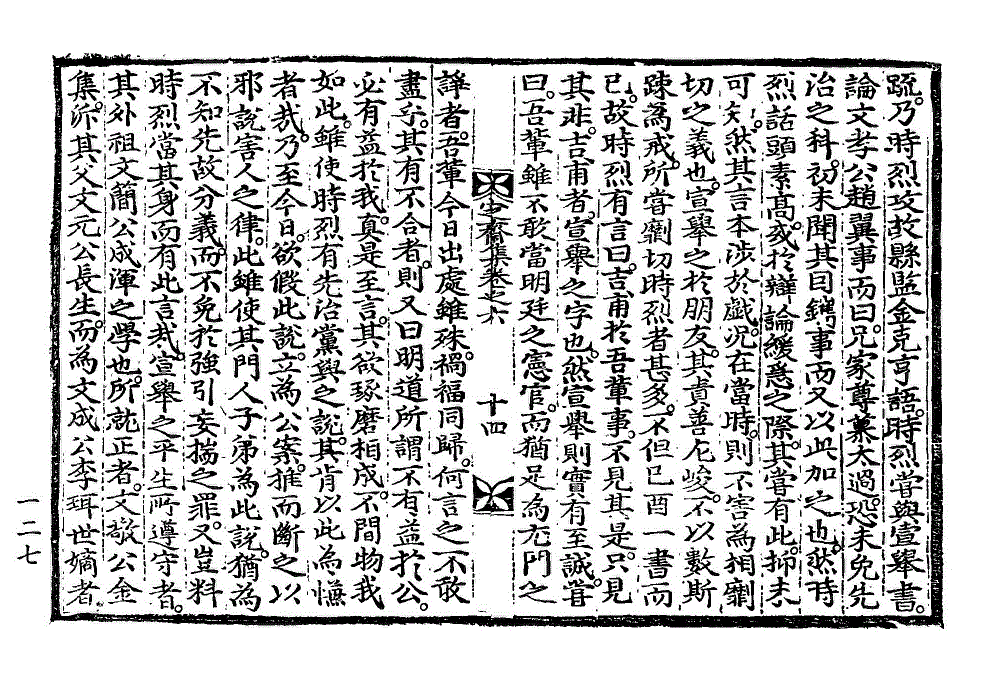 疏。乃时烈攻故县监金克亨语。时烈尝与宣举书。论文孝公赵翼事而曰。兄家尊慕太过。恐未免先治之科。初未闻其因镌(一作鑴)事而又以此加之也。然时烈话头素高。或于辩论缓急之际。其尝有此。抑未可知。然其言本涉于戏。况在当时。则不害为相劘切之义也。宣举之于朋友。其责善尤峻。不以数斯疏为戒。所尝劘切时烈者甚多。不但己酉一书而已。故时烈有言曰。吉甫于吾辈事。不见其是。只见其非。吉甫者。宣举之字也。然宣举则实有至诚。尝曰。吾辈虽不敢当明廷之宪官。而犹足为尤门之诤者。吾辈今日出处虽殊。祸福同归。何言之不敢尽乎。其有不合者。则又曰明道所谓不有益于公。必有益于我。真是至言。其欲琢磨相成。不间物我如此。虽使时烈有先治党与之说。其肯以此为慊者哉。乃至今日。欲假此说。立为公案。推而断之以邪说害人之律。此虽使其门人子弟为此说。犹为不知先故分义。而不免于强引妄揣之罪。又岂料时烈当其身而有此言哉。宣举之平生所遵守者。其外祖文简公成浑之学也。所就正者。文敬公金集。溯其父文元公长生。而为文成公李珥世嫡者
疏。乃时烈攻故县监金克亨语。时烈尝与宣举书。论文孝公赵翼事而曰。兄家尊慕太过。恐未免先治之科。初未闻其因镌(一作鑴)事而又以此加之也。然时烈话头素高。或于辩论缓急之际。其尝有此。抑未可知。然其言本涉于戏。况在当时。则不害为相劘切之义也。宣举之于朋友。其责善尤峻。不以数斯疏为戒。所尝劘切时烈者甚多。不但己酉一书而已。故时烈有言曰。吉甫于吾辈事。不见其是。只见其非。吉甫者。宣举之字也。然宣举则实有至诚。尝曰。吾辈虽不敢当明廷之宪官。而犹足为尤门之诤者。吾辈今日出处虽殊。祸福同归。何言之不敢尽乎。其有不合者。则又曰明道所谓不有益于公。必有益于我。真是至言。其欲琢磨相成。不间物我如此。虽使时烈有先治党与之说。其肯以此为慊者哉。乃至今日。欲假此说。立为公案。推而断之以邪说害人之律。此虽使其门人子弟为此说。犹为不知先故分义。而不免于强引妄揣之罪。又岂料时烈当其身而有此言哉。宣举之平生所遵守者。其外祖文简公成浑之学也。所就正者。文敬公金集。溯其父文元公长生。而为文成公李珥世嫡者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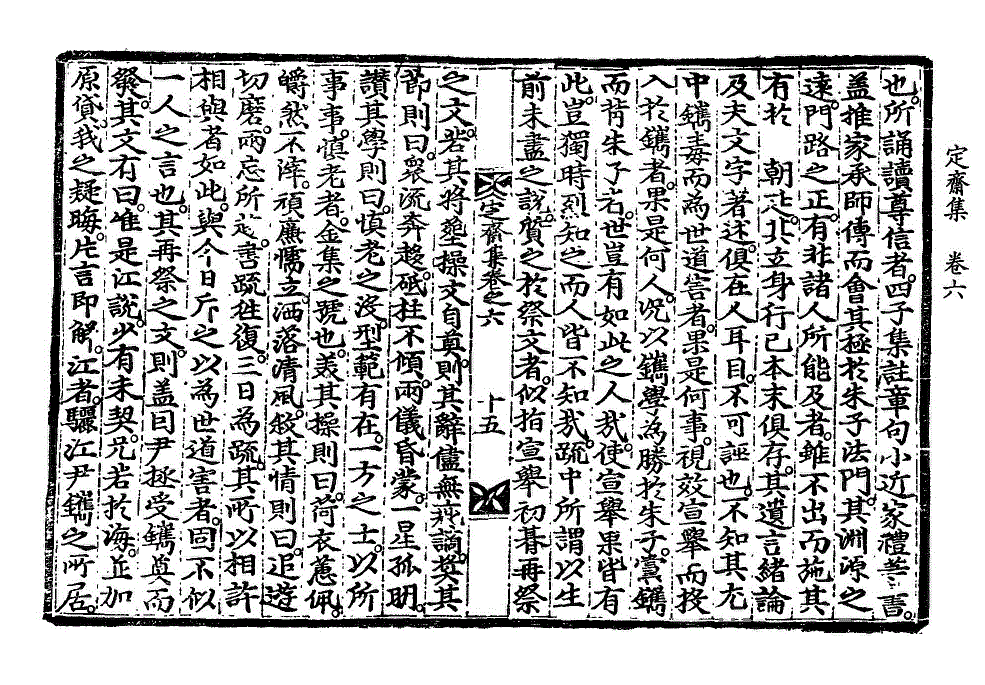 也。所诵读尊信者。四子集注章句小近家礼等书。盖推家承师传而会其极于朱子法门。其渊源之远。门路之正。有非诸人所能及者。虽不出而施其有于 朝廷。其立身行己本末俱存。其遗言绪论及夫文字著述。俱在人耳目。不可诬也。不知其尤中镌(一作鑴)毒而为世道害者。果是何事。视效宣举而投入于镌(一作鑴)者。果是何人。况以镌(一作鑴)学为胜于朱子。党镌(一作鑴)而背朱子者。世岂有如此之人哉。使宣举果皆有此。岂独时烈知之而人皆不知哉。疏中所谓以生前未尽之说。质之于祭文者。似指宣举初期再祭之文。若其将葬操文自奠。则其辞尽无疵谪。奖其节则曰。众流奔趍。砥柱不倾。两仪昏蒙。一星孤明。赞其学则曰。慎老之没。型范有在。一方之士。以所事事。慎老者。金集之号也。美其操则曰。荷衣蕙佩。皭然不滓。顽廉懦立。洒落清风。叙其情则曰。追游切磨。两忘所趍。书疏往复。三日为疏。其所以相许相与者如此。与今日斥之以为世道害者。固不似一人之言也。其再祭之文。则盖因尹拯受镌(一作鑴)奠而发。其文有曰。唯是江说。少有未契。兄若于海。并加原贷。我之疑晦。片言即解。江者。骊江尹镌(一作鑴)之所居。
也。所诵读尊信者。四子集注章句小近家礼等书。盖推家承师传而会其极于朱子法门。其渊源之远。门路之正。有非诸人所能及者。虽不出而施其有于 朝廷。其立身行己本末俱存。其遗言绪论及夫文字著述。俱在人耳目。不可诬也。不知其尤中镌(一作鑴)毒而为世道害者。果是何事。视效宣举而投入于镌(一作鑴)者。果是何人。况以镌(一作鑴)学为胜于朱子。党镌(一作鑴)而背朱子者。世岂有如此之人哉。使宣举果皆有此。岂独时烈知之而人皆不知哉。疏中所谓以生前未尽之说。质之于祭文者。似指宣举初期再祭之文。若其将葬操文自奠。则其辞尽无疵谪。奖其节则曰。众流奔趍。砥柱不倾。两仪昏蒙。一星孤明。赞其学则曰。慎老之没。型范有在。一方之士。以所事事。慎老者。金集之号也。美其操则曰。荷衣蕙佩。皭然不滓。顽廉懦立。洒落清风。叙其情则曰。追游切磨。两忘所趍。书疏往复。三日为疏。其所以相许相与者如此。与今日斥之以为世道害者。固不似一人之言也。其再祭之文。则盖因尹拯受镌(一作鑴)奠而发。其文有曰。唯是江说。少有未契。兄若于海。并加原贷。我之疑晦。片言即解。江者。骊江尹镌(一作鑴)之所居。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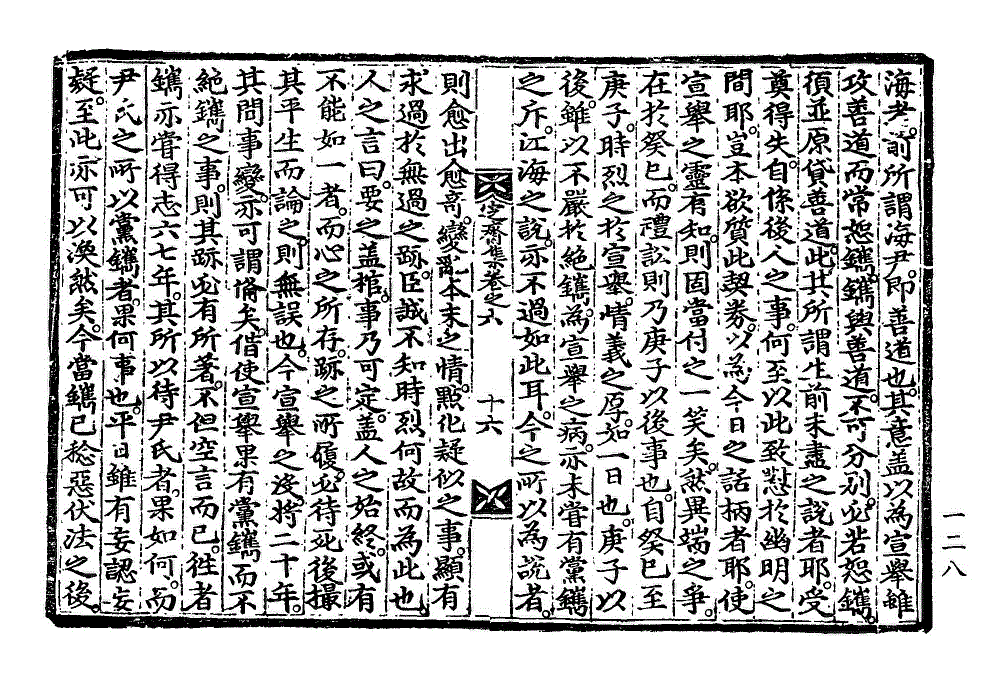 海者。前所谓海尹。即善道也。其意盖以为宣举虽攻善道而常恕镌(一作鑴)。镌(一作鑴)与善道。不可分别。必若恕镌(一作鑴)。须并原贷善道。此其所谓生前未尽之说者耶。受奠得失。自系后人之事。何至以此致怼于幽明之间耶。岂本欲质此契券。以为今日之话柄者耶。使宣举之灵有知。则固当付之一笑矣。然异端之争。在于癸巳。而礼讼则乃庚子以后事也。自癸巳至庚子。时烈之于宣举。情义之厚。如一日也。庚子以后。虽以不严于绝镌(一作鑴)。为宣举之病。亦未尝有党镌(一作鑴)之斥。江海之说。亦不过如此耳。今之所以为说者。则愈出愈奇。变乱本末之情。点化疑似之事。显有求过于无过之迹。臣诚不知时烈何故而为此也。人之言曰。要之盖棺。事乃可定。盖人之始终。或有不能如一者。而心之所存。迹之所履。必待死后撮其平生而论之。则无误也。今宣举之没。将二十年。其间事变。亦可谓备矣。借使宣举果有党镌(一作鑴)而不绝镌(一作鑴)之事。则其迹必有所著。不但空言而已。往者镌(一作鑴)亦尝得志六七年。其所以待尹氏者。果如何。而尹氏之所以党镌(一作鑴)者。果何事也。平日虽有妄认妄疑。至此亦可以涣然矣。今当镌(一作鑴)已稔恶伏法之后。
海者。前所谓海尹。即善道也。其意盖以为宣举虽攻善道而常恕镌(一作鑴)。镌(一作鑴)与善道。不可分别。必若恕镌(一作鑴)。须并原贷善道。此其所谓生前未尽之说者耶。受奠得失。自系后人之事。何至以此致怼于幽明之间耶。岂本欲质此契券。以为今日之话柄者耶。使宣举之灵有知。则固当付之一笑矣。然异端之争。在于癸巳。而礼讼则乃庚子以后事也。自癸巳至庚子。时烈之于宣举。情义之厚。如一日也。庚子以后。虽以不严于绝镌(一作鑴)。为宣举之病。亦未尝有党镌(一作鑴)之斥。江海之说。亦不过如此耳。今之所以为说者。则愈出愈奇。变乱本末之情。点化疑似之事。显有求过于无过之迹。臣诚不知时烈何故而为此也。人之言曰。要之盖棺。事乃可定。盖人之始终。或有不能如一者。而心之所存。迹之所履。必待死后撮其平生而论之。则无误也。今宣举之没。将二十年。其间事变。亦可谓备矣。借使宣举果有党镌(一作鑴)而不绝镌(一作鑴)之事。则其迹必有所著。不但空言而已。往者镌(一作鑴)亦尝得志六七年。其所以待尹氏者。果如何。而尹氏之所以党镌(一作鑴)者。果何事也。平日虽有妄认妄疑。至此亦可以涣然矣。今当镌(一作鑴)已稔恶伏法之后。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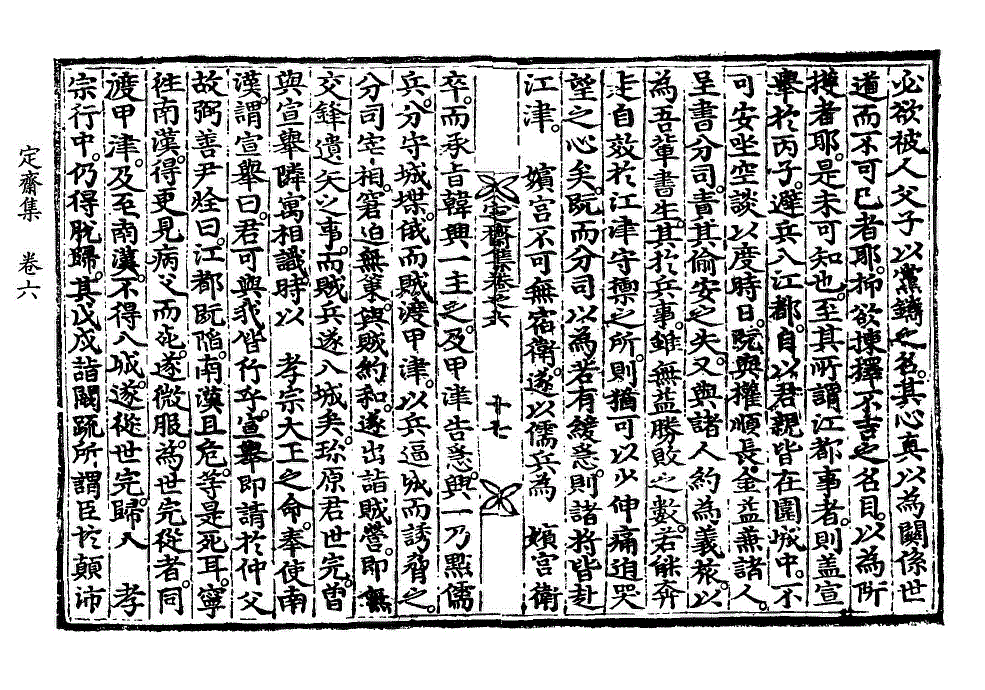 必欲被人父子以党镌(一作鑴)之名。其心真以为关系世道而不可已者耶。抑欲拣择不吉之名目。以为阱擭者耶。是未可知也。至其所谓江都事者。则盖宣举于丙子。避兵入江都。自以君亲皆在围城中。不可安坐空谈以度时日。既与权顺长,金益兼诸人。呈书分司。责其偷安之失。又与诸人约为义旅。以为吾辈书生。其于兵事。虽无益胜败之数。若能奔走自效于江津守御之所。则犹可以少伸痛迫哭望之心矣。既而分司以为若有缓急。则诸将皆赴江津。 嫔宫不可无宿卫。遂以儒兵为 嫔宫卫卒。而承旨韩兴一主之。及甲津告急。兴一乃点儒兵。分守城堞。俄而贼渡甲津。以兵逼城而诱胁之。分司宰相。窘迫无策。与贼约和。遂出诣贼营。即无交锋遗矢之事。而贼兵遂入城矣。珍原君世完。曾与宣举邻寓相识。时以 孝宗大王之命。奉使南汉。谓宣举曰。君可与我偕行乎。宣举即请于仲父故弼善尹烇曰。江都既陷。南汉且危。等是死耳。宁往南汉。得更见病父而死。遂微服。为世完从者。同渡甲津。及至南汉。不得入城。遂从世完。归入 孝宗行中。仍得脱归。其戊戌诣阙疏所谓臣于颠沛
必欲被人父子以党镌(一作鑴)之名。其心真以为关系世道而不可已者耶。抑欲拣择不吉之名目。以为阱擭者耶。是未可知也。至其所谓江都事者。则盖宣举于丙子。避兵入江都。自以君亲皆在围城中。不可安坐空谈以度时日。既与权顺长,金益兼诸人。呈书分司。责其偷安之失。又与诸人约为义旅。以为吾辈书生。其于兵事。虽无益胜败之数。若能奔走自效于江津守御之所。则犹可以少伸痛迫哭望之心矣。既而分司以为若有缓急。则诸将皆赴江津。 嫔宫不可无宿卫。遂以儒兵为 嫔宫卫卒。而承旨韩兴一主之。及甲津告急。兴一乃点儒兵。分守城堞。俄而贼渡甲津。以兵逼城而诱胁之。分司宰相。窘迫无策。与贼约和。遂出诣贼营。即无交锋遗矢之事。而贼兵遂入城矣。珍原君世完。曾与宣举邻寓相识。时以 孝宗大王之命。奉使南汉。谓宣举曰。君可与我偕行乎。宣举即请于仲父故弼善尹烇曰。江都既陷。南汉且危。等是死耳。宁往南汉。得更见病父而死。遂微服。为世完从者。同渡甲津。及至南汉。不得入城。遂从世完。归入 孝宗行中。仍得脱归。其戊戌诣阙疏所谓臣于颠沛定斋集卷之六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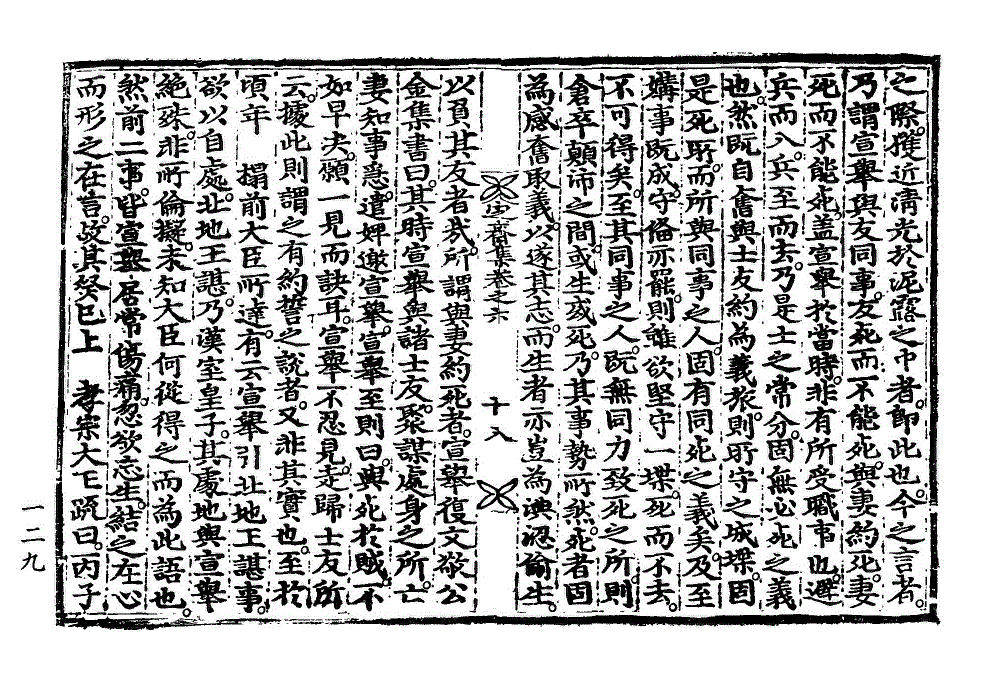 之际。获近清光于泥露之中者。即此也。今之言者。乃谓宣举与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与妻约死。妻死而不能死。盖宣举于当时。非有所受职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是士之常分。固无必死之义也。然既自奋与士友约为义旅。则所守之城堞。固是死所。而所与同事之人。固有同死之义矣。及至媾事既成。守备亦罢。则虽欲坚守一堞。死而不去。不可得矣。至其同事之人。既无同力致死之所。则仓卒颠沛之间。或生或死。乃其事势所然。死者固为感奋取义。以遂其志。而生者亦岂为淟涊偷生。以负其友者哉。所谓与妻约死者。宣举复文敬公金集书曰。其时宣举与诸士友。聚谋处身之所。亡妻知事急。遣婢邀宣举。宣举至则曰。与死于贼。不如早决。愿一见而诀耳。宣举不忍见。走归士友所云。据此则谓之有约誓之说者。又非其实也。至于顷年 榻前大臣所达。有云宣举引北地王谌事。欲以自处。北地王谌。乃汉室皇子。其处地与宣举绝殊。非所伦拟。未知大臣何从得之而为此语也。然前二事。皆宣举居常伤痛。忽欲忘生。结之在心而形之在言。故其癸巳上 孝宗大王疏曰。丙子
之际。获近清光于泥露之中者。即此也。今之言者。乃谓宣举与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与妻约死。妻死而不能死。盖宣举于当时。非有所受职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是士之常分。固无必死之义也。然既自奋与士友约为义旅。则所守之城堞。固是死所。而所与同事之人。固有同死之义矣。及至媾事既成。守备亦罢。则虽欲坚守一堞。死而不去。不可得矣。至其同事之人。既无同力致死之所。则仓卒颠沛之间。或生或死。乃其事势所然。死者固为感奋取义。以遂其志。而生者亦岂为淟涊偷生。以负其友者哉。所谓与妻约死者。宣举复文敬公金集书曰。其时宣举与诸士友。聚谋处身之所。亡妻知事急。遣婢邀宣举。宣举至则曰。与死于贼。不如早决。愿一见而诀耳。宣举不忍见。走归士友所云。据此则谓之有约誓之说者。又非其实也。至于顷年 榻前大臣所达。有云宣举引北地王谌事。欲以自处。北地王谌。乃汉室皇子。其处地与宣举绝殊。非所伦拟。未知大臣何从得之而为此语也。然前二事。皆宣举居常伤痛。忽欲忘生。结之在心而形之在言。故其癸巳上 孝宗大王疏曰。丙子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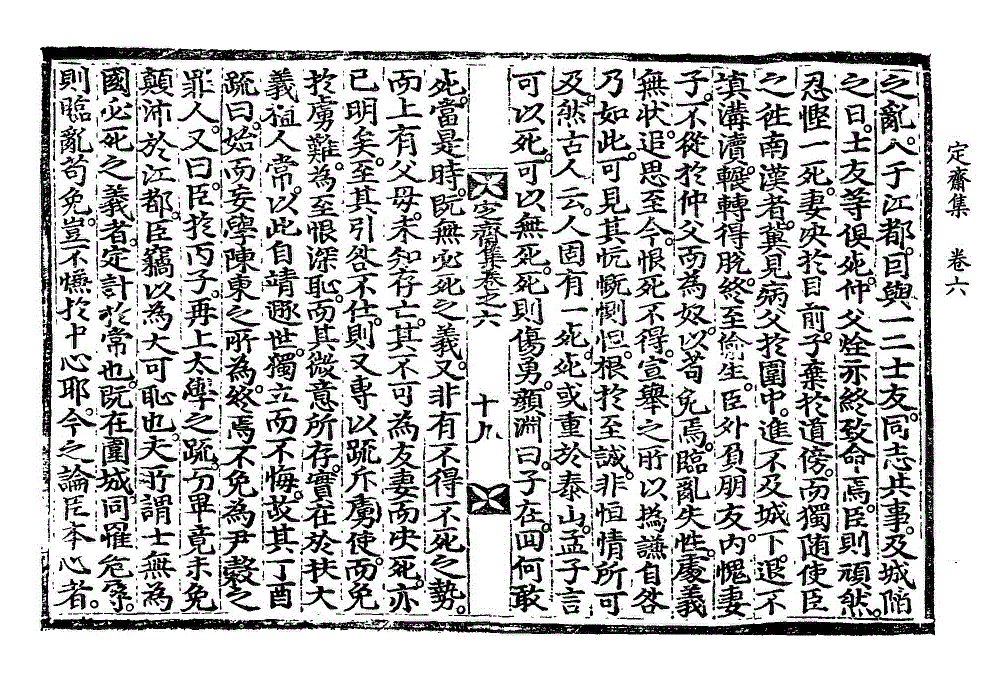 之乱。入于江都。因与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之日。士友等俱死。仲父烇亦终致命焉。臣则顽然。忍悭一死。妻决于目前。子弃于道傍。而独随使臣之往南汉者。冀见病父于围中。进不及城下。退不填沟渎。辗转得脱。终至偷生。臣外负朋友。内愧妻子。不从于仲父而为奴。以苟免焉。临乱失性。处义无状。追思至今。恨死不得。宣举之所以撝谦自咎乃如此。可见其忼慨恻怛。根于至诚。非恒情所可及。然古人云。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孟子言可以死。可以无死。死则伤勇。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当是时。既无必死之义。又非有不得不死之势。而上有父母。未知存亡。其不可为友妻而决死。亦已明矣。至其引咎不仕。则又专以疏斥虏使。而免于虏难。为至恨深耻。而其微意所存。实在于扶大义植人常。以此自靖遁世。独立而不悔。故其丁酉疏曰。始而妄学陈东之所为。终焉不免为尹谷之罪人。又曰。臣于丙子。再上太学之疏。而毕竟未免颠沛于江都。臣窃以为大可耻也。夫所谓士无为国必死之义者。定计于常也。既在围城。同罹危辱。则临乱苟免。岂不慊于中心耶。今之论臣本心者。
之乱。入于江都。因与一二士友。同志共事。及城陷之日。士友等俱死。仲父烇亦终致命焉。臣则顽然。忍悭一死。妻决于目前。子弃于道傍。而独随使臣之往南汉者。冀见病父于围中。进不及城下。退不填沟渎。辗转得脱。终至偷生。臣外负朋友。内愧妻子。不从于仲父而为奴。以苟免焉。临乱失性。处义无状。追思至今。恨死不得。宣举之所以撝谦自咎乃如此。可见其忼慨恻怛。根于至诚。非恒情所可及。然古人云。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孟子言可以死。可以无死。死则伤勇。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当是时。既无必死之义。又非有不得不死之势。而上有父母。未知存亡。其不可为友妻而决死。亦已明矣。至其引咎不仕。则又专以疏斥虏使。而免于虏难。为至恨深耻。而其微意所存。实在于扶大义植人常。以此自靖遁世。独立而不悔。故其丁酉疏曰。始而妄学陈东之所为。终焉不免为尹谷之罪人。又曰。臣于丙子。再上太学之疏。而毕竟未免颠沛于江都。臣窃以为大可耻也。夫所谓士无为国必死之义者。定计于常也。既在围城。同罹危辱。则临乱苟免。岂不慊于中心耶。今之论臣本心者。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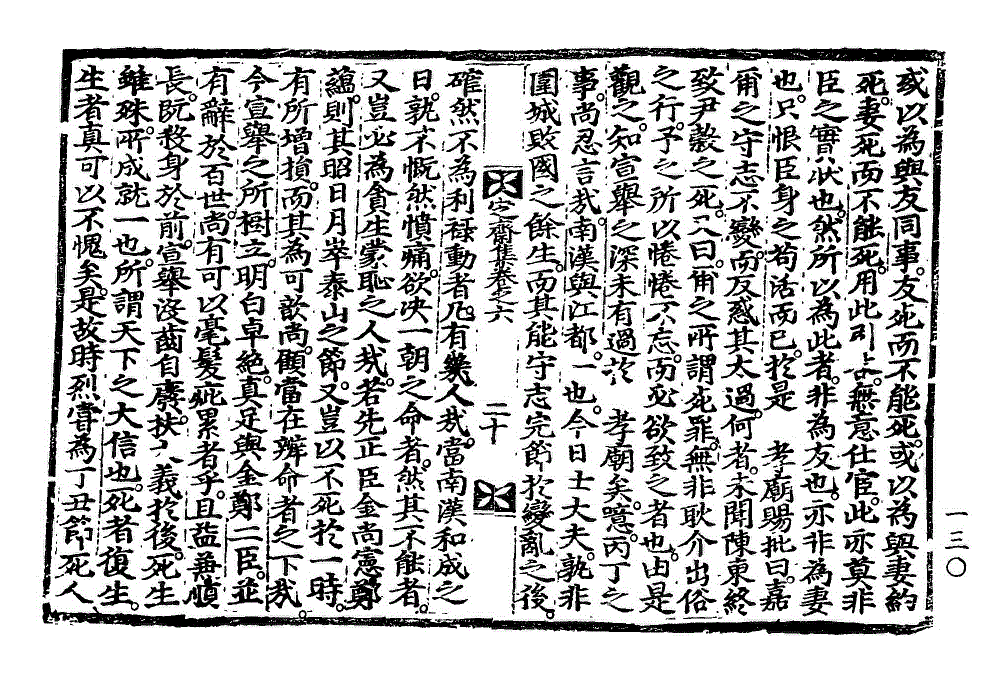 或以为与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或以为与妻约死。妻死而不能死。用此引咎。无意仕宦。此亦莫非臣之实状也。然所以为此者。非为友也。亦非为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于是 孝庙赐批曰。嘉尔之守志不变。而反惑其太过。何者。未闻陈东终致尹谷之死。又曰。尔之所谓死罪。无非耿介出俗之行。予之所以惓惓不忘。而必欲致之者也。由是观之。知宣举之深未有过于 孝庙矣。噫。丙丁之事。尚忍言哉。南汉与江都。一也。今日士大夫。孰非围城败国之馀生。而其能守志完节于变乱之后。确然不为利禄动者。凡有几人哉。当南汉和成之日。孰不慨然愤痛。欲决一朝之命者。然其不能者。又岂必为贪生蒙耻之人哉。若先正臣金尚宪,郑蕴。则其昭日月崒泰山之节。又岂以不死于一时。有所增损。而其为可歆尚。顾当在辨命者之下哉。今宣举之所树立。明白卓绝。真足与金郑二臣。并有辞于百世。尚有可以毫发疵累者乎。且益兼,顺长。既杀身于前。宣举没齿自废。扶大义于后。死生虽殊。所成就一也。所谓天下之大信也。死者复生。生者真可以不愧矣。是故时烈尝为丁丑节死人
或以为与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或以为与妻约死。妻死而不能死。用此引咎。无意仕宦。此亦莫非臣之实状也。然所以为此者。非为友也。亦非为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于是 孝庙赐批曰。嘉尔之守志不变。而反惑其太过。何者。未闻陈东终致尹谷之死。又曰。尔之所谓死罪。无非耿介出俗之行。予之所以惓惓不忘。而必欲致之者也。由是观之。知宣举之深未有过于 孝庙矣。噫。丙丁之事。尚忍言哉。南汉与江都。一也。今日士大夫。孰非围城败国之馀生。而其能守志完节于变乱之后。确然不为利禄动者。凡有几人哉。当南汉和成之日。孰不慨然愤痛。欲决一朝之命者。然其不能者。又岂必为贪生蒙耻之人哉。若先正臣金尚宪,郑蕴。则其昭日月崒泰山之节。又岂以不死于一时。有所增损。而其为可歆尚。顾当在辨命者之下哉。今宣举之所树立。明白卓绝。真足与金郑二臣。并有辞于百世。尚有可以毫发疵累者乎。且益兼,顺长。既杀身于前。宣举没齿自废。扶大义于后。死生虽殊。所成就一也。所谓天下之大信也。死者复生。生者真可以不愧矣。是故时烈尝为丁丑节死人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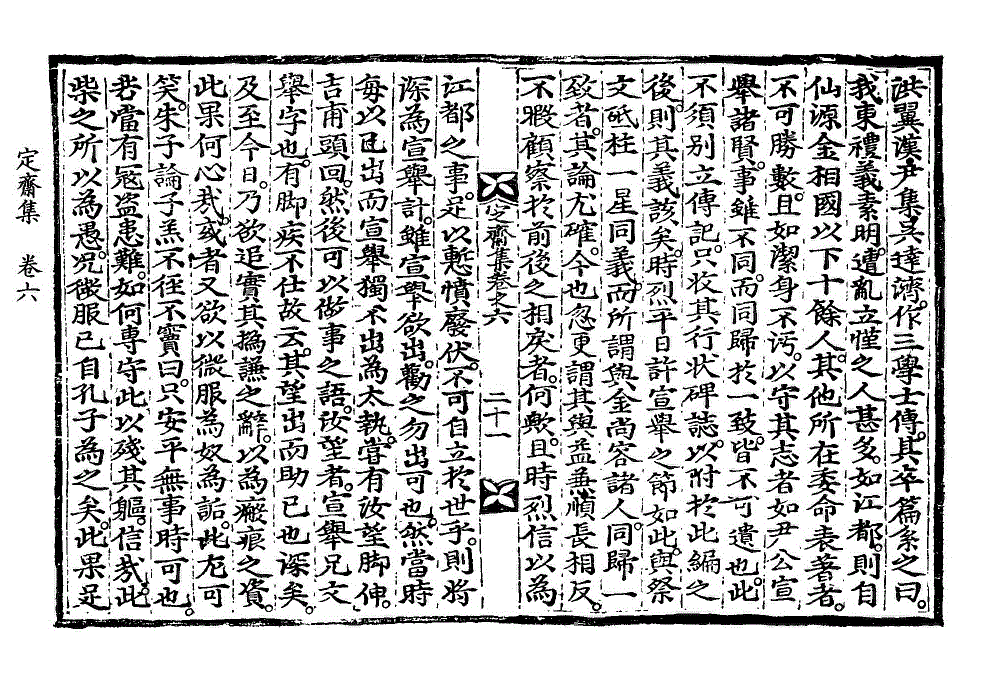 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作三学士传。其卒篇系之曰。我东礼义素明。遭乱立慬之人甚多。如江都。则自仙源金相国以下十馀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胜数。且如洁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举诸贤。事虽不同。而同归于一致。皆不可遗也。此不须别立传记。只收其行状碑志。以附于此编之后。则其义该矣。时烈平日许宣举之节如此。与祭文砥柱一星同义。而所谓与金尚容诸人。同归一致者。其论尤确。今也忽更谓其与益兼,顺长相反。不暇顾察于前后之相戾者。何欤。且时烈信以为江都之事。足以惭愤废伏。不可自立于世乎。则将深为宣举计。虽宣举欲出。劝之勿出可也。然当时每以己出而宣举独不出为太执。尝有汝望脚伸。吉甫头回。然后可以做事之语。汝望者。宣举兄文举字也。有脚疾不仕故云。其望出而助己也深矣。及至今日。乃欲追实其撝谦之辞。以为瘢痕之资。此果何心哉。或者又欲以微服为奴为诟。此尤可笑。朱子论子羔不径不窦曰。只安平无事时可也。若当有寇盗患难。如何专守此以残其躯。信哉。此柴之所以为愚。况微服已自孔子为之矣。此果足
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作三学士传。其卒篇系之曰。我东礼义素明。遭乱立慬之人甚多。如江都。则自仙源金相国以下十馀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胜数。且如洁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举诸贤。事虽不同。而同归于一致。皆不可遗也。此不须别立传记。只收其行状碑志。以附于此编之后。则其义该矣。时烈平日许宣举之节如此。与祭文砥柱一星同义。而所谓与金尚容诸人。同归一致者。其论尤确。今也忽更谓其与益兼,顺长相反。不暇顾察于前后之相戾者。何欤。且时烈信以为江都之事。足以惭愤废伏。不可自立于世乎。则将深为宣举计。虽宣举欲出。劝之勿出可也。然当时每以己出而宣举独不出为太执。尝有汝望脚伸。吉甫头回。然后可以做事之语。汝望者。宣举兄文举字也。有脚疾不仕故云。其望出而助己也深矣。及至今日。乃欲追实其撝谦之辞。以为瘢痕之资。此果何心哉。或者又欲以微服为奴为诟。此尤可笑。朱子论子羔不径不窦曰。只安平无事时可也。若当有寇盗患难。如何专守此以残其躯。信哉。此柴之所以为愚。况微服已自孔子为之矣。此果足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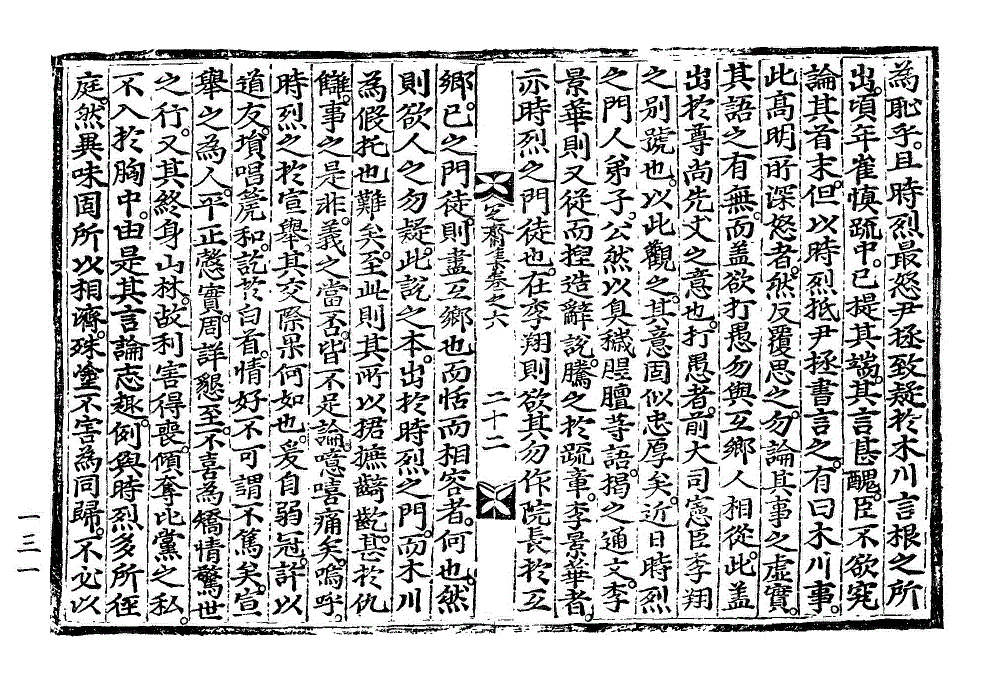 为耻乎。且时烈最怒尹拯致疑于木川言根之所出。顷年崔慎疏中。已提其端。其言甚丑。臣不欲究论其首末。但以时烈抵尹拯书言之。有曰木川事。此高明所深怒者。然反覆思之。勿论其事之虚实。其语之有无。而盖欲打愚勿与互乡人相从。此盖出于尊尚先丈之意也。打愚者。前大司宪臣李翔之别号也。以此观之。其意固似忠厚矣。近日时烈之门人弟子。公然以臭秽腥膻等语。揭之通文。李景华则又从而捏造辞说。腾之于疏章。李景华者。亦时烈之门徒也。在李翔则欲其勿作院长于互乡。己之门徒。则尽互乡也而恬而相容者。何也。然则欲人之勿疑。此说之本。出于时烈之门。而木川为假托也难矣。至此则其所以捃摭齮龁。甚于仇雠。事之是非。义之当否。皆不足论。噫嘻痛矣。呜呼。时烈之于宣举。其交际果何如也。爰自弱冠。许以道友。埙唱篪和。讫于白首。情好不可谓不笃矣。宣举之为人。平正悫实。周详恳至。不喜为矫情惊世之行。又其终身山林。故利害得丧。倾夺比党之私。不入于胸中。由是其言论志趣。例与时烈多所径庭。然异味固所以相济。殊涂不害为同归。不必以
为耻乎。且时烈最怒尹拯致疑于木川言根之所出。顷年崔慎疏中。已提其端。其言甚丑。臣不欲究论其首末。但以时烈抵尹拯书言之。有曰木川事。此高明所深怒者。然反覆思之。勿论其事之虚实。其语之有无。而盖欲打愚勿与互乡人相从。此盖出于尊尚先丈之意也。打愚者。前大司宪臣李翔之别号也。以此观之。其意固似忠厚矣。近日时烈之门人弟子。公然以臭秽腥膻等语。揭之通文。李景华则又从而捏造辞说。腾之于疏章。李景华者。亦时烈之门徒也。在李翔则欲其勿作院长于互乡。己之门徒。则尽互乡也而恬而相容者。何也。然则欲人之勿疑。此说之本。出于时烈之门。而木川为假托也难矣。至此则其所以捃摭齮龁。甚于仇雠。事之是非。义之当否。皆不足论。噫嘻痛矣。呜呼。时烈之于宣举。其交际果何如也。爰自弱冠。许以道友。埙唱篪和。讫于白首。情好不可谓不笃矣。宣举之为人。平正悫实。周详恳至。不喜为矫情惊世之行。又其终身山林。故利害得丧。倾夺比党之私。不入于胸中。由是其言论志趣。例与时烈多所径庭。然异味固所以相济。殊涂不害为同归。不必以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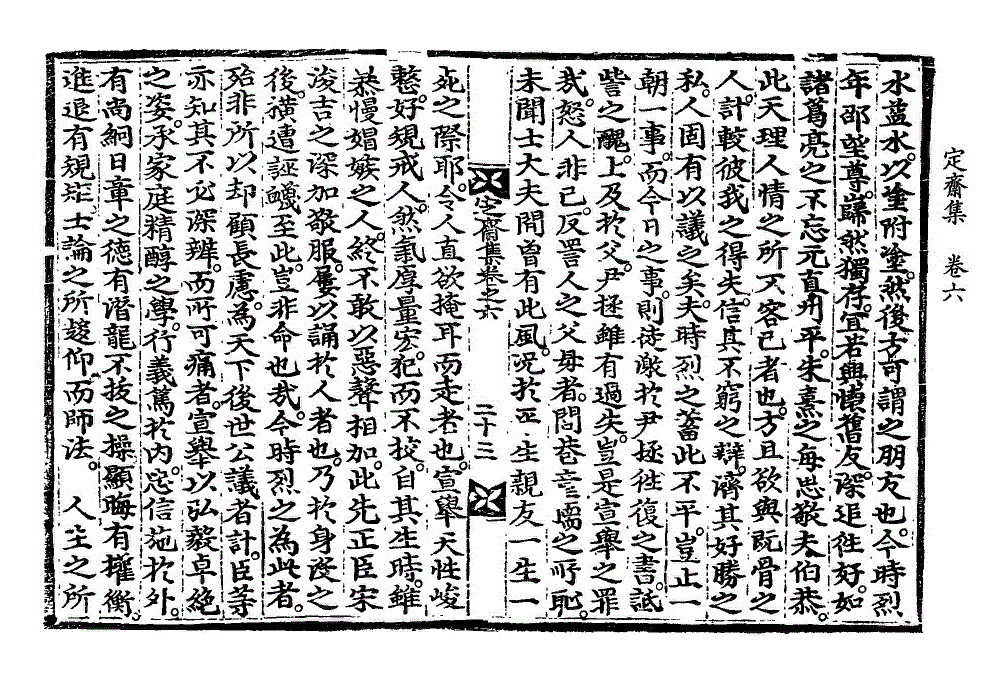 水益水。以涂附涂。然后方可谓之朋友也。今时烈年邵(一作卲)望尊。岿然独存。宜若兴怀旧友。深追往好。如诸葛亮之不忘元直,州平。朱熹之每思敬夫,伯恭。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方且欲与既骨之人。计较彼我之得失。信其不穷之辩。济其好胜之私。人固有以议之矣。夫时烈之蓄此不平。岂止一朝一事。而今日之事。则徒激于尹拯往复之书。诋訾之丑。上及于父。尹拯虽有过失。岂是宣举之罪哉。怒人非己。反詈人之父母者。闾巷童孺之所耻。未闻士大夫间曾有此风。况于平生亲友一生一死之际耶。令人直欲掩耳而走者也。宣举天性峻整。好规戒人。然气厚量宏。犯而不挍。自其生时。虽暴慢媢嫉之人。终不敢以恶声相加。此先正臣宋浚吉之深加敬服。屡以诵于人者也。乃于身没之后。横遭诬蔑至此。岂非命也哉。今时烈之为此者。殆非所以却顾长虑。为天下后世公议者计。臣等亦知其不必深辨。而所可痛者。宣举以弘毅卓绝之姿。承家庭精醇之学。行义笃于内。忠信施于外。有尚絅日章之德。有潜龙不拔之操。显晦有权衡。进退有规矩。士论之所趍仰而师法。 人主之所
水益水。以涂附涂。然后方可谓之朋友也。今时烈年邵(一作卲)望尊。岿然独存。宜若兴怀旧友。深追往好。如诸葛亮之不忘元直,州平。朱熹之每思敬夫,伯恭。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方且欲与既骨之人。计较彼我之得失。信其不穷之辩。济其好胜之私。人固有以议之矣。夫时烈之蓄此不平。岂止一朝一事。而今日之事。则徒激于尹拯往复之书。诋訾之丑。上及于父。尹拯虽有过失。岂是宣举之罪哉。怒人非己。反詈人之父母者。闾巷童孺之所耻。未闻士大夫间曾有此风。况于平生亲友一生一死之际耶。令人直欲掩耳而走者也。宣举天性峻整。好规戒人。然气厚量宏。犯而不挍。自其生时。虽暴慢媢嫉之人。终不敢以恶声相加。此先正臣宋浚吉之深加敬服。屡以诵于人者也。乃于身没之后。横遭诬蔑至此。岂非命也哉。今时烈之为此者。殆非所以却顾长虑。为天下后世公议者计。臣等亦知其不必深辨。而所可痛者。宣举以弘毅卓绝之姿。承家庭精醇之学。行义笃于内。忠信施于外。有尚絅日章之德。有潜龙不拔之操。显晦有权衡。进退有规矩。士论之所趍仰而师法。 人主之所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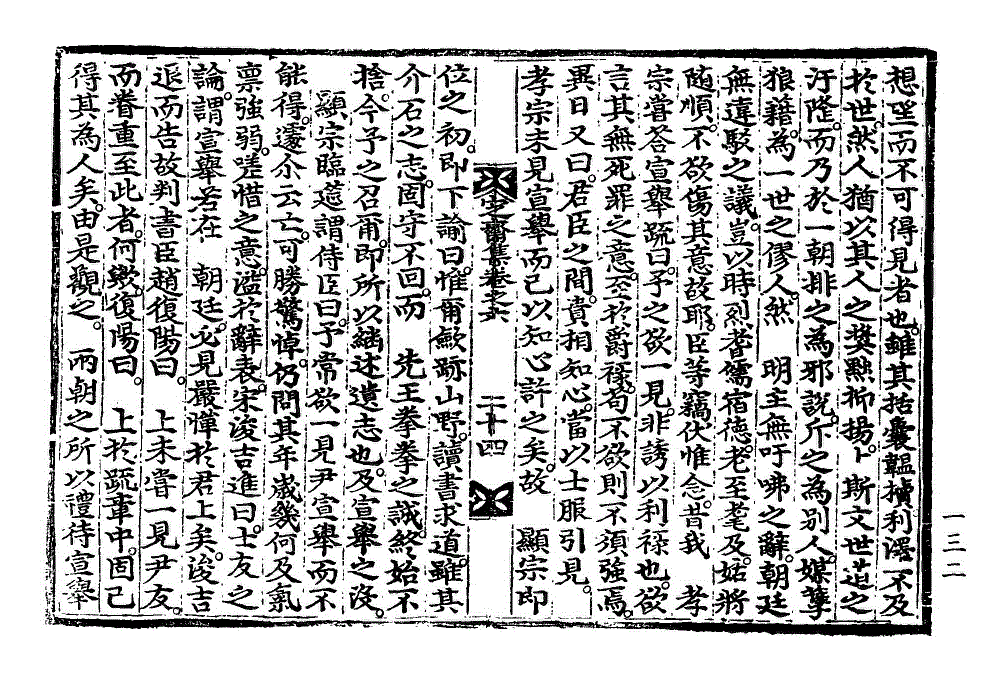 想望而不可得见者也。虽其括囊韫椟。利泽不及于世。然人犹以其人之奖黜抑扬。卜斯文世道之污隆。而乃于一朝排之为邪说。斥之为别人。媒孽狼藉。为一世之僇人。然 明主无吁咈之辞。朝廷无违驳之议。岂以时烈耆儒宿德。老至耄及。姑将随顺。不欲伤其意故耶。臣等窃伏惟念。昔我 孝宗尝答宣举疏曰。予之欲一见。非诱以利禄也。欲言其无死罪之意。至于爵禄。苟不欲则不须强焉。异日又曰。君臣之间。贵相知心。当以士服引见。 孝宗未见宣举而已以知心许之矣。故 显宗即位之初。即下谕曰。惟尔敛迹山野。读书求道。虽其介石之志。固守不回。而 先王拳拳之诚。终始不舍。今予之召尔。即所以继述遗志也。及宣举之没。 显宗临筵谓侍臣曰。予常欲一见尹宣举而不能得。遽尔云亡。可胜惊悼。仍问其年岁几何及气禀强弱。嗟惜之意。溢于辞表。宋浚吉进曰。士友之论。谓宣举若在 朝廷。必见严惮于君上矣。浚吉退而告故判书臣赵复阳曰。 上未尝一见尹友。而眷重至此者。何欤。复阳曰。 上于疏章中。固已得其为人矣。由是观之。 两朝之所以礼待宣举
想望而不可得见者也。虽其括囊韫椟。利泽不及于世。然人犹以其人之奖黜抑扬。卜斯文世道之污隆。而乃于一朝排之为邪说。斥之为别人。媒孽狼藉。为一世之僇人。然 明主无吁咈之辞。朝廷无违驳之议。岂以时烈耆儒宿德。老至耄及。姑将随顺。不欲伤其意故耶。臣等窃伏惟念。昔我 孝宗尝答宣举疏曰。予之欲一见。非诱以利禄也。欲言其无死罪之意。至于爵禄。苟不欲则不须强焉。异日又曰。君臣之间。贵相知心。当以士服引见。 孝宗未见宣举而已以知心许之矣。故 显宗即位之初。即下谕曰。惟尔敛迹山野。读书求道。虽其介石之志。固守不回。而 先王拳拳之诚。终始不舍。今予之召尔。即所以继述遗志也。及宣举之没。 显宗临筵谓侍臣曰。予常欲一见尹宣举而不能得。遽尔云亡。可胜惊悼。仍问其年岁几何及气禀强弱。嗟惜之意。溢于辞表。宋浚吉进曰。士友之论。谓宣举若在 朝廷。必见严惮于君上矣。浚吉退而告故判书臣赵复阳曰。 上未尝一见尹友。而眷重至此者。何欤。复阳曰。 上于疏章中。固已得其为人矣。由是观之。 两朝之所以礼待宣举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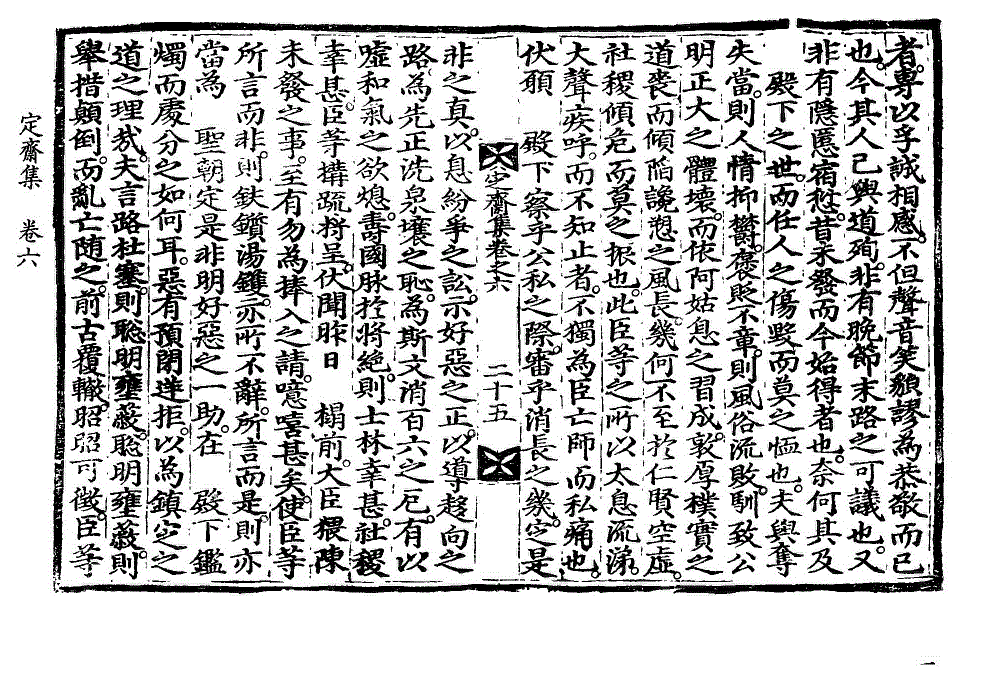 者。专以孚诚相感。不但声音笑貌谬为恭敬而已也。今其人已与道殉。非有晚节末路之可议也。又非有隐慝宿愆。昔未发而今始得者也。奈何其及 殿下之世。而任人之伤毁而莫之恤也。夫与夺失当。则人情抑郁。褒贬不章。则风俗流败。驯致公明正大之体坏。而依阿姑息之习成。敦厚朴实之道丧。而倾陷谗愬之风长。几何不至于仁贤空虚。社稷倾危而莫之振也。此臣等之所以太息流涕。大声疾呼。而不知止者。不独为臣亡师而私痛也。伏愿 殿下察乎公私之际。审乎消长之几。定是非之真。以息纷争之讼。示好恶之正。以导趍向之路。为先正洗泉壤之耻。为斯文消百六之厄。有以嘘和气之欲熄。寿国脉于将绝。则士林幸甚。社稷幸甚。臣等搆疏将呈。伏闻昨日 榻前。大臣猥陈未发之事。至有勿为捧入之请。噫嘻甚矣。使臣等所言而非。则鈇锧汤镬。亦所不辞。所言而是。则亦当为 圣朝定是非明好恶之一助。在 殿下鉴烛而处分之如何耳。恶有预闭逆拒。以为镇定之道之理哉。夫言路杜塞。则聪明壅蔽。聪明壅蔽。则举措颠倒。而乱亡随之。前古覆辙。昭昭可徵。臣等
者。专以孚诚相感。不但声音笑貌谬为恭敬而已也。今其人已与道殉。非有晚节末路之可议也。又非有隐慝宿愆。昔未发而今始得者也。奈何其及 殿下之世。而任人之伤毁而莫之恤也。夫与夺失当。则人情抑郁。褒贬不章。则风俗流败。驯致公明正大之体坏。而依阿姑息之习成。敦厚朴实之道丧。而倾陷谗愬之风长。几何不至于仁贤空虚。社稷倾危而莫之振也。此臣等之所以太息流涕。大声疾呼。而不知止者。不独为臣亡师而私痛也。伏愿 殿下察乎公私之际。审乎消长之几。定是非之真。以息纷争之讼。示好恶之正。以导趍向之路。为先正洗泉壤之耻。为斯文消百六之厄。有以嘘和气之欲熄。寿国脉于将绝。则士林幸甚。社稷幸甚。臣等搆疏将呈。伏闻昨日 榻前。大臣猥陈未发之事。至有勿为捧入之请。噫嘻甚矣。使臣等所言而非。则鈇锧汤镬。亦所不辞。所言而是。则亦当为 圣朝定是非明好恶之一助。在 殿下鉴烛而处分之如何耳。恶有预闭逆拒。以为镇定之道之理哉。夫言路杜塞。则聪明壅蔽。聪明壅蔽。则举措颠倒。而乱亡随之。前古覆辙。昭昭可徵。臣等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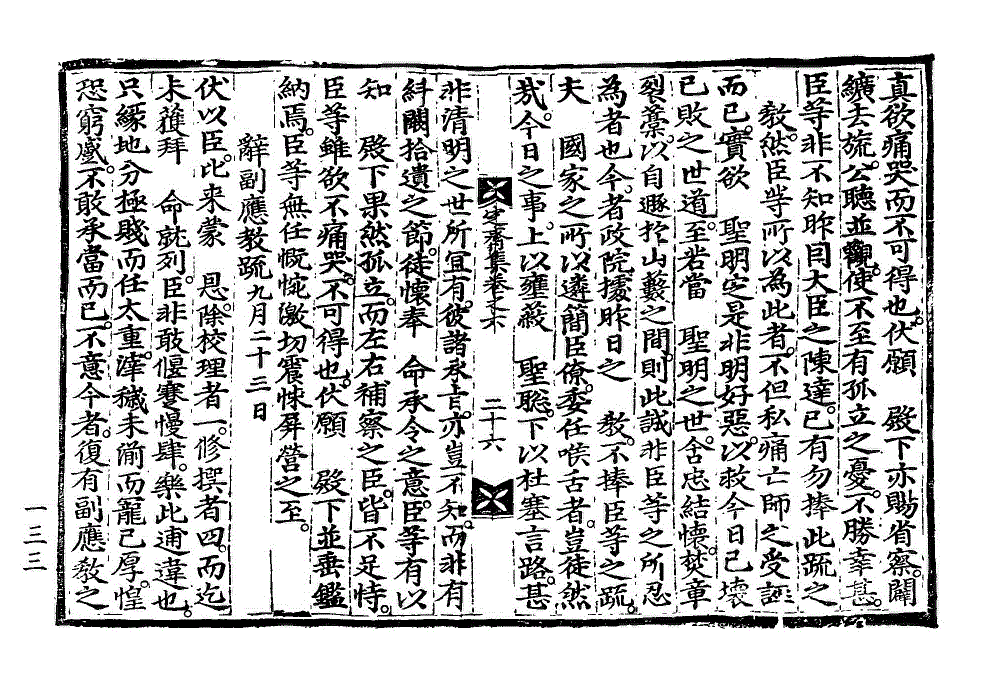 真欲痛哭而不可得也。伏愿 殿下亦赐省察。辟纩去旒。公听并观。使不至有孤立之忧。不胜幸甚。臣等非不知昨因大臣之陈达。已有勿捧此疏之 教。然臣等所以为此者。不但私痛亡师之受诬而已。实欲 圣明定是非明好恶。以救今日已坏已败之世道。至若当 圣明之世。含忠结怀。焚章裂藁。以自遁于山薮之间。则此诚非臣等之所忍为者也。今者政院据昨日之 教。不捧臣等之疏。夫 国家之所以遴简臣僚。委任喉舌者。岂徒然哉。今日之事。上以壅蔽 圣聪。下以杜塞言路。甚非清明之世所宜有。彼诸承旨。亦岂不知。而非有纠阙拾遗之节。徒怀奉 命承令之意。臣等有以知 殿下果然孤立。而左右补察之臣。皆不足恃。臣等虽欲不痛哭。不可得也。伏愿 殿下并垂鉴纳焉。臣等无任慨惋激切震悚屏营之至。
真欲痛哭而不可得也。伏愿 殿下亦赐省察。辟纩去旒。公听并观。使不至有孤立之忧。不胜幸甚。臣等非不知昨因大臣之陈达。已有勿捧此疏之 教。然臣等所以为此者。不但私痛亡师之受诬而已。实欲 圣明定是非明好恶。以救今日已坏已败之世道。至若当 圣明之世。含忠结怀。焚章裂藁。以自遁于山薮之间。则此诚非臣等之所忍为者也。今者政院据昨日之 教。不捧臣等之疏。夫 国家之所以遴简臣僚。委任喉舌者。岂徒然哉。今日之事。上以壅蔽 圣聪。下以杜塞言路。甚非清明之世所宜有。彼诸承旨。亦岂不知。而非有纠阙拾遗之节。徒怀奉 命承令之意。臣等有以知 殿下果然孤立。而左右补察之臣。皆不足恃。臣等虽欲不痛哭。不可得也。伏愿 殿下并垂鉴纳焉。臣等无任慨惋激切震悚屏营之至。辞副应教疏(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臣。比来蒙 恩。除校理者一。修撰者四。而迄未获拜 命就列。臣非敢偃蹇慢肆。乐此逋违也。只缘地分极贱而任太重。滓秽未湔而宠已厚。惶恐穷蹙。不敢承当而已。不意今者。复有副应教之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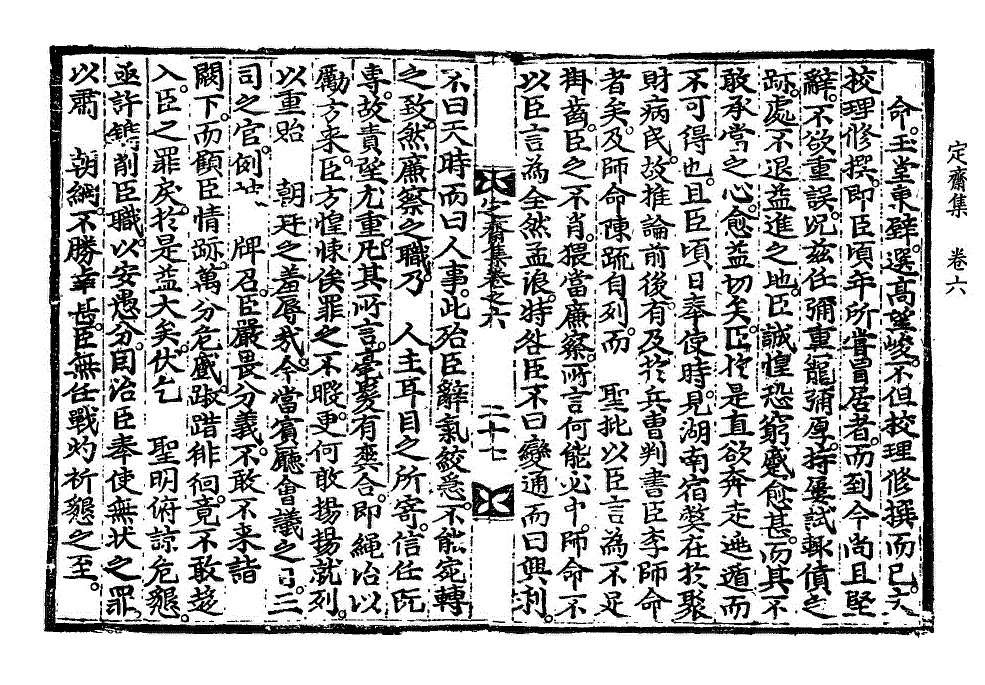 命。玉堂东壁。选高望峻。不但校理修撰而已。夫校理修撰。即臣顷年所尝冒居者。而到今尚且坚辞。不欲重误。况玆任弥重宠弥厚。持屡试辄偾之迹。处不退益进之地。臣诚惶恐穷蹙愈甚。而其不敢承当之心。愈益切矣。臣于是直欲奔走逃遁而不可得也。且臣顷日奉使时。见湖南宿弊在于聚财病民。故推论前后。有及于兵曹判书臣李师命者矣。及师命陈疏自列。而 圣批以臣言为不足挂齿。臣之不肖。猥当廉察。所言何能必中。师命不以臣言为全然孟浪。特咎臣不曰变通而曰兴利。不曰天时而曰人事。此殆臣辞气绞急。不能宛转之致。然廉察之职。乃 人主耳目之所寄。信任既专。故责望尤重。凡其所言。毫发有爽合。即绳治以励方来。臣方惶悚俟罪之不暇。更何敢扬扬就列。以重贻 朝廷之羞辱哉。今当宾厅会议之日。三司之官。例被 牌召。臣严畏分义。不敢不来诣 阙下。而顾臣情迹。万分危蹙。踧踖徘徊。竟不敢趍入。臣之罪戾。于是益大矣。伏乞 圣明俯谅危恳。亟许镌削臣职。以安愚分。因治臣奉使无状之罪。以肃 朝纲。不胜幸甚。臣无任战灼祈恳之至。
命。玉堂东壁。选高望峻。不但校理修撰而已。夫校理修撰。即臣顷年所尝冒居者。而到今尚且坚辞。不欲重误。况玆任弥重宠弥厚。持屡试辄偾之迹。处不退益进之地。臣诚惶恐穷蹙愈甚。而其不敢承当之心。愈益切矣。臣于是直欲奔走逃遁而不可得也。且臣顷日奉使时。见湖南宿弊在于聚财病民。故推论前后。有及于兵曹判书臣李师命者矣。及师命陈疏自列。而 圣批以臣言为不足挂齿。臣之不肖。猥当廉察。所言何能必中。师命不以臣言为全然孟浪。特咎臣不曰变通而曰兴利。不曰天时而曰人事。此殆臣辞气绞急。不能宛转之致。然廉察之职。乃 人主耳目之所寄。信任既专。故责望尤重。凡其所言。毫发有爽合。即绳治以励方来。臣方惶悚俟罪之不暇。更何敢扬扬就列。以重贻 朝廷之羞辱哉。今当宾厅会议之日。三司之官。例被 牌召。臣严畏分义。不敢不来诣 阙下。而顾臣情迹。万分危蹙。踧踖徘徊。竟不敢趍入。臣之罪戾。于是益大矣。伏乞 圣明俯谅危恳。亟许镌削臣职。以安愚分。因治臣奉使无状之罪。以肃 朝纲。不胜幸甚。臣无任战灼祈恳之至。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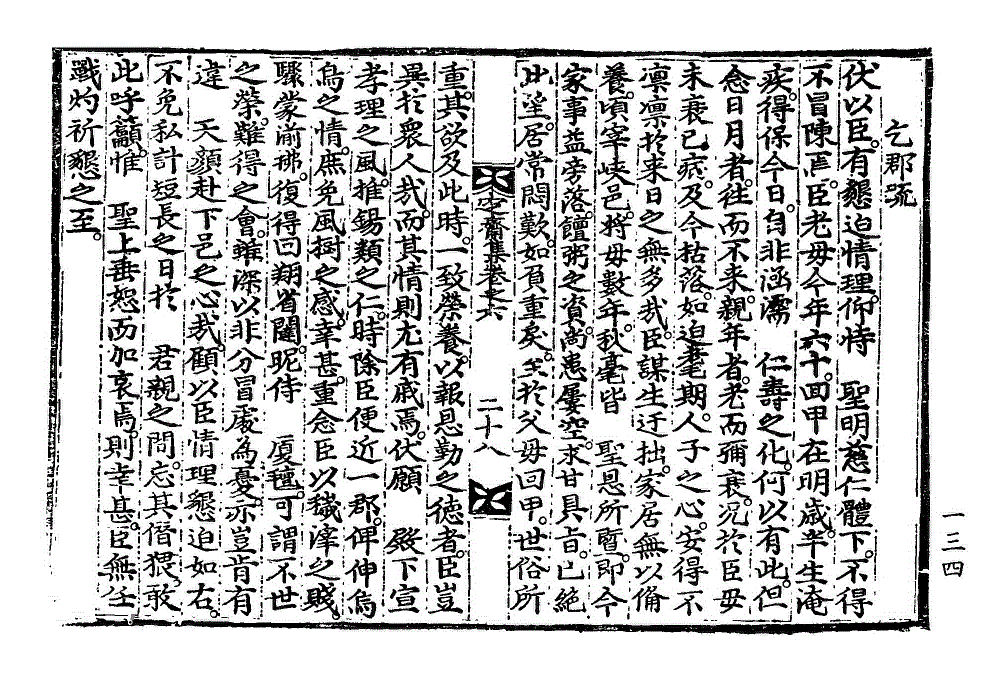 乞郡疏
乞郡疏伏以臣。有恳迫情理。仰恃 圣明慈仁体下。不得不冒陈焉。臣老母今年六十。回甲在明岁。半生淹疾。得保今日。自非涵濡 仁寿之化。何以有此。但念日月者。往而不来。亲年者。老而弥衰。况于臣母未衰已病。及今枯落。如迫耄期。人子之心。安得不凛凛于来日之无多哉。臣谋生迂拙。家居无以备养。顷宰峡邑。将母数年。秋毫皆 圣恩所暨。即今家事益旁落。饘粥之资。尚患屡空。求甘具旨。已绝此望。居常闷叹。如负重戾。至于父母回甲。世俗所重。其欲及此时。一致荣养。以报恩勤之德者。臣岂异于众人哉。而其情则尤有戚焉。伏愿 殿下宣孝理之风。推锡类之仁。时除臣便近一郡。俾伸乌鸟之情。庶免风树之感。幸甚。重念臣以秽滓之贱。骤蒙湔拂。复得回翔省闼。昵侍 厦毡。可谓不世之荣。难得之会。虽深以非分冒处为忧。亦岂肯有违 天颜赴下邑之心哉。顾以臣情理恳迫如右。不免私计短长之日于 君亲之间。忘其僭猥。敢此呼吁。惟 圣上垂恕而加哀焉。则幸甚。臣无任战灼祈恳之至。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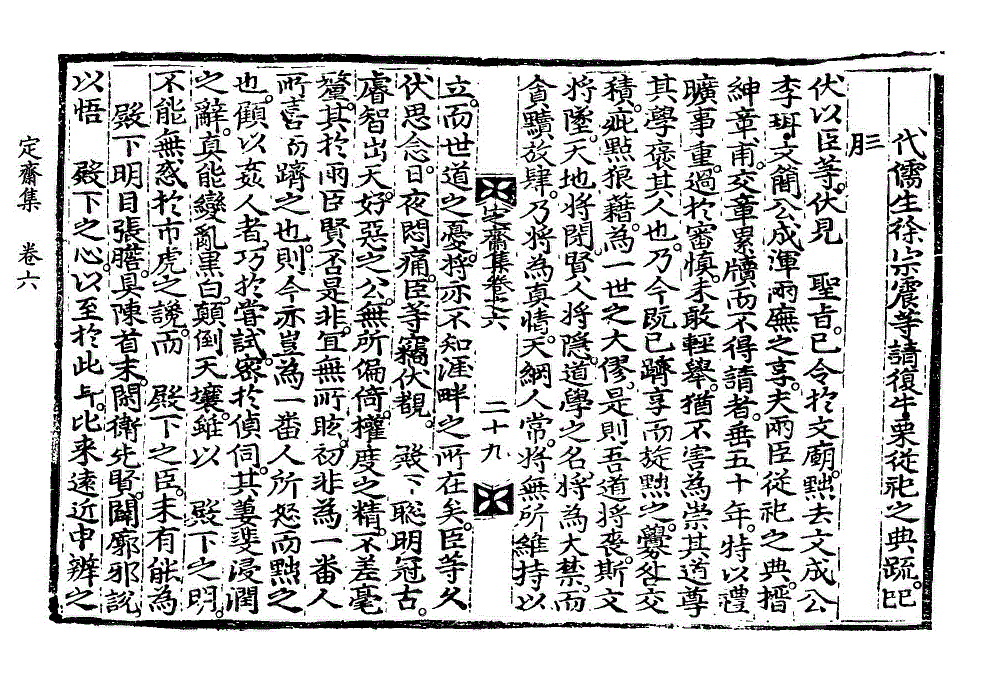 代儒生徐宗震等请复牛,栗从祀之典疏。(己巳三月)
代儒生徐宗震等请复牛,栗从祀之典疏。(己巳三月)伏以臣等。伏见 圣旨。已令于文庙。黜去文成公李珥,文简公成浑两庑之享。夫两臣从祀之典。搢绅章甫。交章累牍而不得请者。垂五十年。特以礼旷事重。过于审慎。未敢轻举。犹不害为崇其道尊其学褒其人也。乃今既已跻享而旋黜之。衅咎交积。疵点狼藉。为一世之大僇。是则吾道将丧。斯文将坠。天地将闭。贤人将隐。道学之名。将为大禁。而贪黩放肆。乃将为真情。天纲人常。将无所维持以立。而世道之忧。将亦不知涯畔之所在矣。臣等久伏思念。日夜闷痛。臣等窃伏睹。 殿下聪明冠古。睿智出天。好恶之公。无所偏倚。权度之精。不差毫釐。其于两臣贤否是非。宜无所眩。初非为一番人所喜而跻之也。则今亦岂为一番人所怒而黜之也。顾以奸人者。巧于尝试。密于侦伺。其萋斐浸润之辞。真能变乱黑白。颠倒天壤。虽以 殿下之明。不能无惑于韨虎之谗。而 殿下之臣。未有能为 殿下明目张胆。具陈首末。闲卫先贤。辟廓邪说。以悟 殿下之心。以至于此耳。比来远近申辨之
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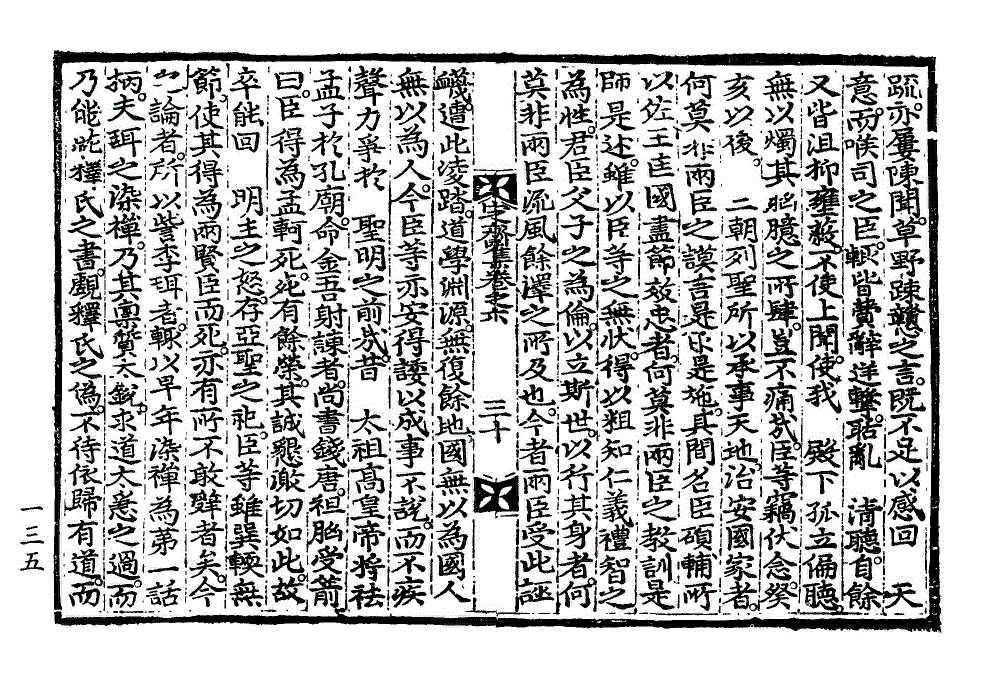 疏。亦屡陈闻。草野疏戆之言。既不足以感回 天意。而喉司之臣。辄皆费辞逆击。聒乱 清听。自馀又皆沮抑壅蔽。不使上闻。使我 殿下孤立偏听。无以烛其胸臆之所肆。岂不痛哉。臣等窃伏念。癸亥以后。 二朝列圣所以承事天地。治安国家者。何莫非两臣之谟言是取是施。其间名臣硕辅所以佐王匡国尽节效忠者。何莫非两臣之教训是师是述。虽以臣等之无状。得以粗知仁义礼智之为性。君臣父子之为伦。以立斯世。以行其身者。何莫非两臣流风馀泽之所及也。今者两臣受此诬蔑。遭此凌踏。道学渊源。无复馀地。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今臣等亦安得诿以成事不说。而不疾声力争于 圣明之前哉。昔 太祖高皇帝将祛孟子于孔庙。命金吾射谏者。尚书钱唐。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馀荣。其诚恳激切如此。故卒能回 明主之怒。存亚圣之祀。臣等虽巽软无节。使其得为两贤臣而死。亦有所不敢辞者矣。今之论者。所以訾李珥者。辄以早年染禅为第一话柄。夫珥之染禅。乃其禀质太锐。求道太急之过。而乃能就释氏之书。觑释氏之伪。不待依归有道。而
疏。亦屡陈闻。草野疏戆之言。既不足以感回 天意。而喉司之臣。辄皆费辞逆击。聒乱 清听。自馀又皆沮抑壅蔽。不使上闻。使我 殿下孤立偏听。无以烛其胸臆之所肆。岂不痛哉。臣等窃伏念。癸亥以后。 二朝列圣所以承事天地。治安国家者。何莫非两臣之谟言是取是施。其间名臣硕辅所以佐王匡国尽节效忠者。何莫非两臣之教训是师是述。虽以臣等之无状。得以粗知仁义礼智之为性。君臣父子之为伦。以立斯世。以行其身者。何莫非两臣流风馀泽之所及也。今者两臣受此诬蔑。遭此凌踏。道学渊源。无复馀地。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今臣等亦安得诿以成事不说。而不疾声力争于 圣明之前哉。昔 太祖高皇帝将祛孟子于孔庙。命金吾射谏者。尚书钱唐。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馀荣。其诚恳激切如此。故卒能回 明主之怒。存亚圣之祀。臣等虽巽软无节。使其得为两贤臣而死。亦有所不敢辞者矣。今之论者。所以訾李珥者。辄以早年染禅为第一话柄。夫珥之染禅。乃其禀质太锐。求道太急之过。而乃能就释氏之书。觑释氏之伪。不待依归有道。而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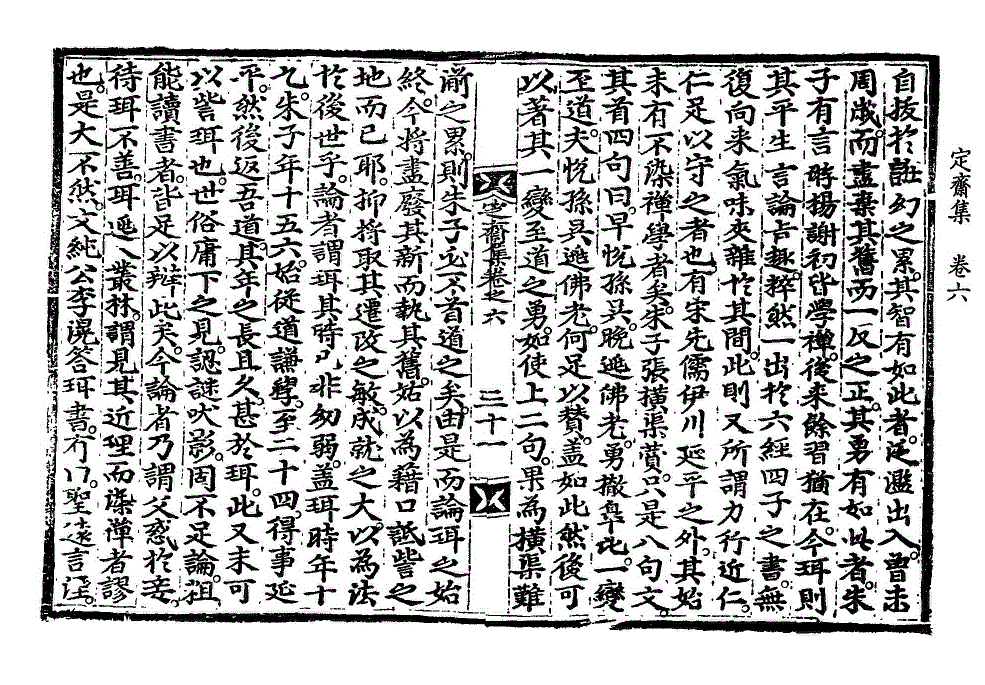 自拔于诳幻之累。其智有如此者。泛滥出入。曾未周岁。而尽弃其旧而一反之正。其勇有如此者。朱子有言游扬谢初皆学禅。后来馀习犹在。今珥则其平生言论旨趣。粹然一出于六经四子之书。无复向来气味夹杂于其间。此则又所谓力行近仁。仁足以守之者也。有宋先儒伊川延平之外。其始未有不染禅学者矣。朱子张横渠赞。只是八句文。其首四句曰。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夫悦孙吴逃佛老。何足以赞。盖如此然后可以著其一变至道之勇。如使上二句。果为横渠难湔之累。则朱子必不首道之矣。由是而论珥之始终。今将尽废其新而执其旧。姑以为藉口诋訾之地而已耶。抑将取其迁改之敏。成就之大。以为法于后世乎。论者谓珥其时已非幼弱。盖珥时年十九。朱子年十五六。始从道谦学。至二十四。得事延平。然后返吾道。其年之长且久。甚于珥。此又未可以訾珥也。世俗庸下之见。认谜吠影。固不足论。粗能读书者。皆足以辨此矣。今论者乃谓父惑于妾。待珥不善。珥逃入丛林。谓见其近理而染禅者谬也。是大不然。文纯公李滉答珥书。有曰。圣远言湮。
自拔于诳幻之累。其智有如此者。泛滥出入。曾未周岁。而尽弃其旧而一反之正。其勇有如此者。朱子有言游扬谢初皆学禅。后来馀习犹在。今珥则其平生言论旨趣。粹然一出于六经四子之书。无复向来气味夹杂于其间。此则又所谓力行近仁。仁足以守之者也。有宋先儒伊川延平之外。其始未有不染禅学者矣。朱子张横渠赞。只是八句文。其首四句曰。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夫悦孙吴逃佛老。何足以赞。盖如此然后可以著其一变至道之勇。如使上二句。果为横渠难湔之累。则朱子必不首道之矣。由是而论珥之始终。今将尽废其新而执其旧。姑以为藉口诋訾之地而已耶。抑将取其迁改之敏。成就之大。以为法于后世乎。论者谓珥其时已非幼弱。盖珥时年十九。朱子年十五六。始从道谦学。至二十四。得事延平。然后返吾道。其年之长且久。甚于珥。此又未可以訾珥也。世俗庸下之见。认谜吠影。固不足论。粗能读书者。皆足以辨此矣。今论者乃谓父惑于妾。待珥不善。珥逃入丛林。谓见其近理而染禅者谬也。是大不然。文纯公李滉答珥书。有曰。圣远言湮。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6L 页
 异端乱真。古之聪明才杰之士。始终迷溺者。固不足论矣。惟程张朱诸先生。其始若不能无少出入。而旋觉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脱洪流而返真源也哉。往闻人言足下读释氏书。颇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来见我也。不讳其实而能言其非。吾知足下之可与适道也。以此观之。谓珥见其近理而染禅者。固李滉之说也。滉之于珥。既以不讳其实许之。其间岂有底蕴之不尽哉。今如论者之说。则珥幼年之事。直是丧性狂走。及其改图之后。滉与其洁而不保其往。可也。所谓谈释氏中其毒者。果何事。而程张朱之出入。又何足论哉。信流俗哓吪之传。而弁髦先正之定论。宁有此理哉。所谓父妾待珥不善。诚有此事。珥庶母性至悖。珥尽诚事之。一如亲母。负罪引慝。以适其意。晚年其母感化。反为善人。及珥之没。服丧三年。今之论者。谓珥所遭。乃人伦之变。夫尽烝乂之实。革凶悖之性者。乃珥遇变善处。至行美德。所遭之不幸。又岂珥之罪哉。其谓珥毁形变名者。尤无所据。文忠公臣张维漫笔所记金玄成,李谨诚所传珥初出山时发长委地。髻大如拳。及李有庆丁亥封事
异端乱真。古之聪明才杰之士。始终迷溺者。固不足论矣。惟程张朱诸先生。其始若不能无少出入。而旋觉其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脱洪流而返真源也哉。往闻人言足下读释氏书。颇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来见我也。不讳其实而能言其非。吾知足下之可与适道也。以此观之。谓珥见其近理而染禅者。固李滉之说也。滉之于珥。既以不讳其实许之。其间岂有底蕴之不尽哉。今如论者之说。则珥幼年之事。直是丧性狂走。及其改图之后。滉与其洁而不保其往。可也。所谓谈释氏中其毒者。果何事。而程张朱之出入。又何足论哉。信流俗哓吪之传。而弁髦先正之定论。宁有此理哉。所谓父妾待珥不善。诚有此事。珥庶母性至悖。珥尽诚事之。一如亲母。负罪引慝。以适其意。晚年其母感化。反为善人。及珥之没。服丧三年。今之论者。谓珥所遭。乃人伦之变。夫尽烝乂之实。革凶悖之性者。乃珥遇变善处。至行美德。所遭之不幸。又岂珥之罪哉。其谓珥毁形变名者。尤无所据。文忠公臣张维漫笔所记金玄成,李谨诚所传珥初出山时发长委地。髻大如拳。及李有庆丁亥封事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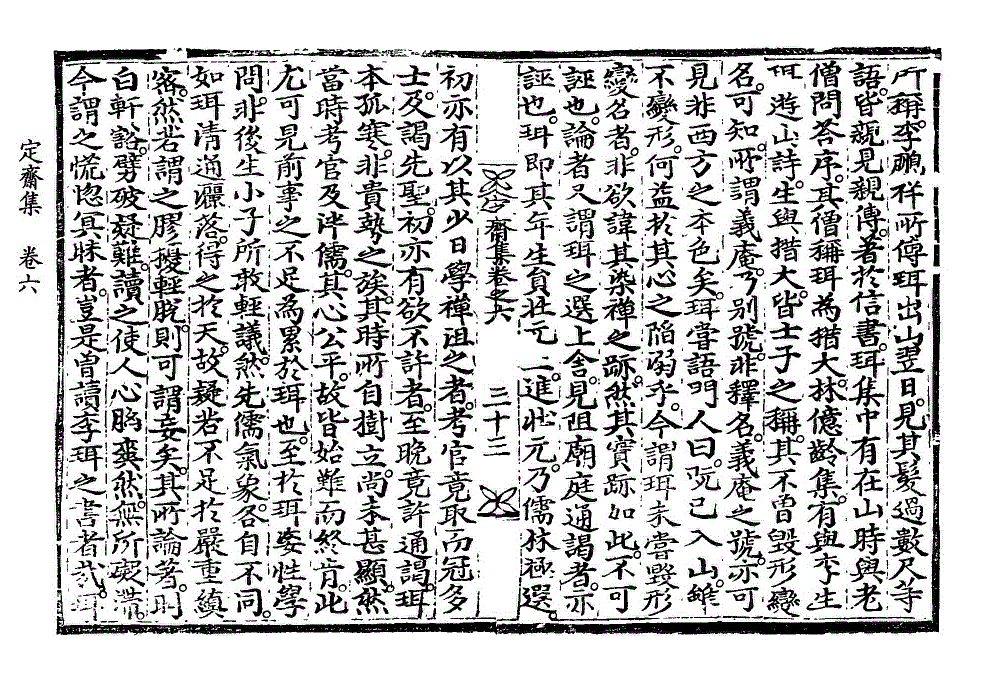 所称。李鹏祥所传珥出山翌日。见其发过数尺等语。皆亲见亲传。著于信书。珥集中有在山时与老僧问答序。其僧称珥为措大。林亿龄集。有与李生珥游山诗。生与措大。皆士子之称。其不曾毁形变名。可知。所谓义庵。乃别号。非释名。义庵之号。亦可见非西方之本色矣。珥尝语门人曰。既已入山。虽不变形。何益于其心之陷溺乎。今谓珥未尝毁形变名者。非欲讳其染禅之迹。然其实迹如此。不可诬也。论者又谓珥之选上舍。见阻庙庭通谒者。亦诬也。珥即其年生员壮元。生进壮元。乃儒林极选。初亦有以其少日学禅沮之者。考官竟取而冠多士。及谒先圣。初亦有欲不许者。至晚竟许通谒。珥本孤寒。非贵势之族。其时所自树立。尚未甚显。然当时考官及泮儒。其心公平。故皆始难而终肯。此尤可见前事之不足为累于珥也。至于珥姿性学问。非后生小子所敢轻议。然先儒气象。各自不同。如珥清通洒落。得之于天。故疑若不足于严重缜密。然若谓之胶扰轻脱。则可谓妄矣。其所论著。明白轩豁。劈破疑难。读之使人心胸爽然。无所碍滞。今谓之慌惚冥昧者。岂是曾读李珥之书者哉。珥
所称。李鹏祥所传珥出山翌日。见其发过数尺等语。皆亲见亲传。著于信书。珥集中有在山时与老僧问答序。其僧称珥为措大。林亿龄集。有与李生珥游山诗。生与措大。皆士子之称。其不曾毁形变名。可知。所谓义庵。乃别号。非释名。义庵之号。亦可见非西方之本色矣。珥尝语门人曰。既已入山。虽不变形。何益于其心之陷溺乎。今谓珥未尝毁形变名者。非欲讳其染禅之迹。然其实迹如此。不可诬也。论者又谓珥之选上舍。见阻庙庭通谒者。亦诬也。珥即其年生员壮元。生进壮元。乃儒林极选。初亦有以其少日学禅沮之者。考官竟取而冠多士。及谒先圣。初亦有欲不许者。至晚竟许通谒。珥本孤寒。非贵势之族。其时所自树立。尚未甚显。然当时考官及泮儒。其心公平。故皆始难而终肯。此尤可见前事之不足为累于珥也。至于珥姿性学问。非后生小子所敢轻议。然先儒气象。各自不同。如珥清通洒落。得之于天。故疑若不足于严重缜密。然若谓之胶扰轻脱。则可谓妄矣。其所论著。明白轩豁。劈破疑难。读之使人心胸爽然。无所碍滞。今谓之慌惚冥昧者。岂是曾读李珥之书者哉。珥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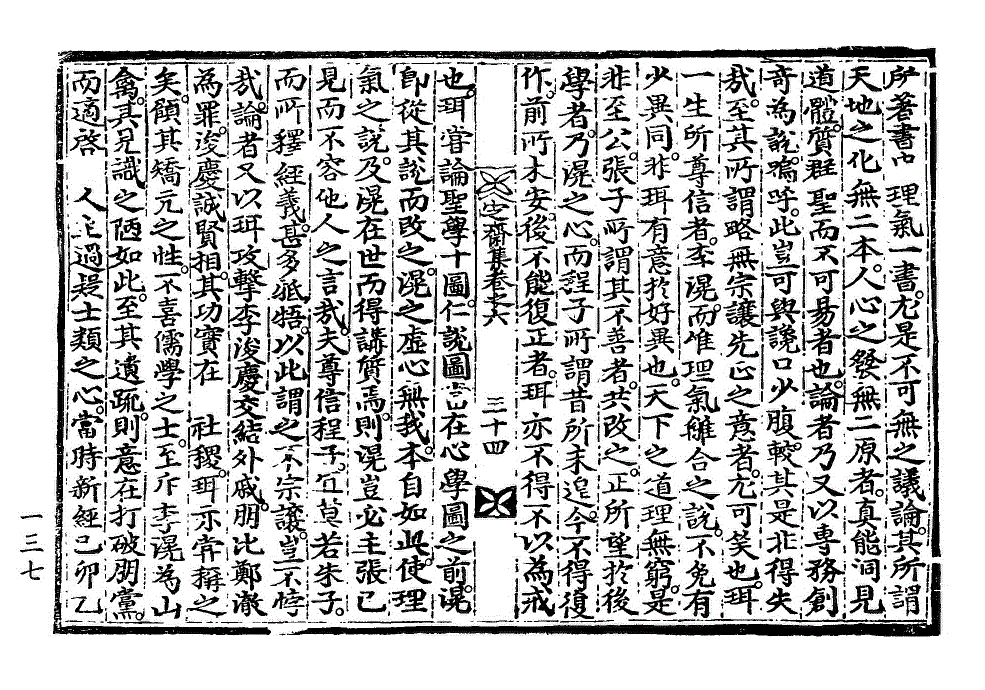 所著书中理气一书。尤是不可无之议论。其所谓天地之化无二本。人心之发无二原者。真能洞见道体。质群圣而不可易者也。论者乃又以专务创奇为说。呜呼。此岂可与谗口少腹。较其是非得失哉。至其所谓略无宗让先正之意者。尤可笑也。珥一生所尊信者。李滉。而唯理气离合之说。不免有少异同。非珥有意于好异也。天下之道理无穷。是非至公。张子所谓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者。乃滉之心。而程子所谓昔所未遑。今不得复作。前所未安。后不能复正者。珥亦不得不以为戒也。珥尝论圣学十图。仁说图当在心学图之前。滉即从其说而改之。滉之虚心无我。本自如此。使理气之说。及滉在世而得讲质焉。则滉岂必主张己见而不容他人之言哉。夫尊信程子。宜莫若朱子。而所释经义。甚多牴牾。以此谓之不宗让。岂不悖哉。论者又以珥攻击李浚庆交结外戚。朋比郑澈为罪。浚庆诚贤相。其功实在 社稷。珥亦尝称之矣。顾其矫亢之性。不喜儒学之士。至斥李滉为山禽。其见识之陋如此。至其遗疏。则意在打破朋党。而适启 人主过疑士类之心。当时新经己卯乙
所著书中理气一书。尤是不可无之议论。其所谓天地之化无二本。人心之发无二原者。真能洞见道体。质群圣而不可易者也。论者乃又以专务创奇为说。呜呼。此岂可与谗口少腹。较其是非得失哉。至其所谓略无宗让先正之意者。尤可笑也。珥一生所尊信者。李滉。而唯理气离合之说。不免有少异同。非珥有意于好异也。天下之道理无穷。是非至公。张子所谓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者。乃滉之心。而程子所谓昔所未遑。今不得复作。前所未安。后不能复正者。珥亦不得不以为戒也。珥尝论圣学十图。仁说图当在心学图之前。滉即从其说而改之。滉之虚心无我。本自如此。使理气之说。及滉在世而得讲质焉。则滉岂必主张己见而不容他人之言哉。夫尊信程子。宜莫若朱子。而所释经义。甚多牴牾。以此谓之不宗让。岂不悖哉。论者又以珥攻击李浚庆交结外戚。朋比郑澈为罪。浚庆诚贤相。其功实在 社稷。珥亦尝称之矣。顾其矫亢之性。不喜儒学之士。至斥李滉为山禽。其见识之陋如此。至其遗疏。则意在打破朋党。而适启 人主过疑士类之心。当时新经己卯乙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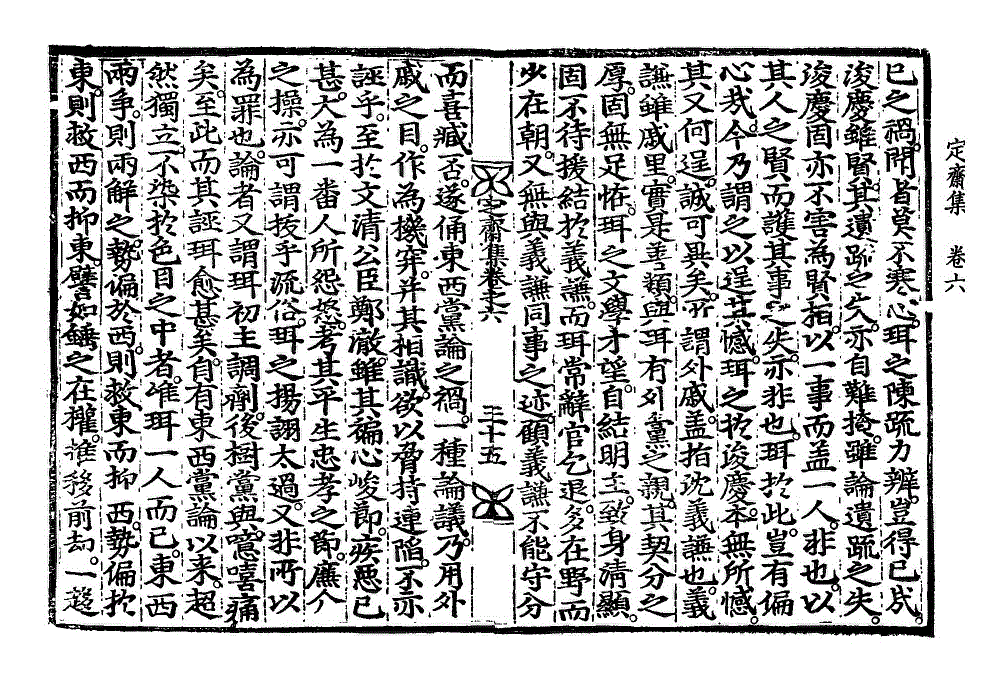 巳之祸。闻者莫不寒心。珥之陈疏力辨。岂得已哉。浚庆虽贤。其遗疏之失。亦自难掩。虽论遗疏之失。浚庆固亦不害为贤相。以一事而盖一人。非也。以其人之贤而护其事之失。亦非也。珥于此。岂有偏心哉。今乃谓之以逞其憾。珥之于浚庆。本无所憾。其又何逞。诚可异矣。所谓外戚。盖指沈义谦也。义谦虽戚里。实是善类。与珥有外党之亲。其契分之厚。固无足怪。珥之文学才望。自结明主。致身清显。固不待援结于义谦。而珥常辞官乞退。多在野而少在朝。又无与义谦同事之迹。顾义谦不能守分而喜臧否。遂俑东西党论之祸。一种论议。乃用外戚之目。作为机阱。并其相识。欲以胁持连陷。不亦诬乎。至于文清公臣郑澈。虽其褊心峻节。疾恶已甚。大为一番人所怨怒。考其平生忠孝之节。廉介之操。亦可谓拔乎流俗。珥之扬诩太过。又非所以为罪也。论者又谓珥初主调剂。后树党与。噫嘻痛矣。至此而其诬珥愈甚矣。自有东西党论以来。超然独立。不染于色目之中者。唯珥一人而已。东西两争。则两解之。势偏于西。则救东而抑西。势偏于东。则救西而抑东。譬如锤之在权。推移前却。一趍
巳之祸。闻者莫不寒心。珥之陈疏力辨。岂得已哉。浚庆虽贤。其遗疏之失。亦自难掩。虽论遗疏之失。浚庆固亦不害为贤相。以一事而盖一人。非也。以其人之贤而护其事之失。亦非也。珥于此。岂有偏心哉。今乃谓之以逞其憾。珥之于浚庆。本无所憾。其又何逞。诚可异矣。所谓外戚。盖指沈义谦也。义谦虽戚里。实是善类。与珥有外党之亲。其契分之厚。固无足怪。珥之文学才望。自结明主。致身清显。固不待援结于义谦。而珥常辞官乞退。多在野而少在朝。又无与义谦同事之迹。顾义谦不能守分而喜臧否。遂俑东西党论之祸。一种论议。乃用外戚之目。作为机阱。并其相识。欲以胁持连陷。不亦诬乎。至于文清公臣郑澈。虽其褊心峻节。疾恶已甚。大为一番人所怨怒。考其平生忠孝之节。廉介之操。亦可谓拔乎流俗。珥之扬诩太过。又非所以为罪也。论者又谓珥初主调剂。后树党与。噫嘻痛矣。至此而其诬珥愈甚矣。自有东西党论以来。超然独立。不染于色目之中者。唯珥一人而已。东西两争。则两解之。势偏于西。则救东而抑西。势偏于东。则救西而抑东。譬如锤之在权。推移前却。一趍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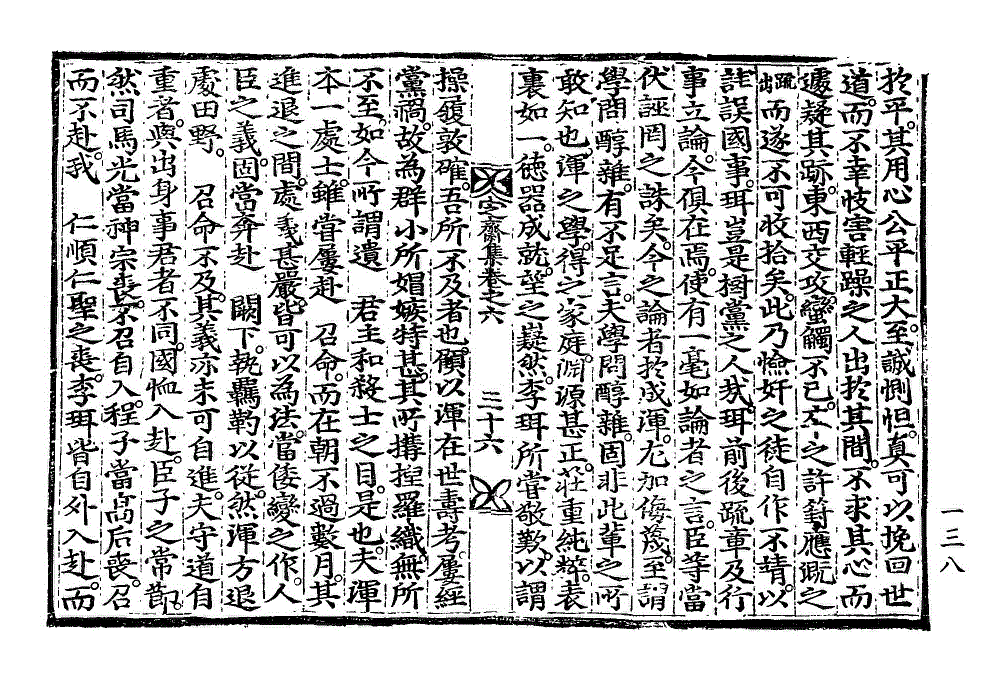 于平。其用心公平正大。至诚恻怛。真可以挽回世道。而不幸忮害轻躁之人出于其间。不求其心而遽疑其迹。东西交攻。蛮触不已。卒之许篈,应溉之疏出而遂不可收拾矣。此乃憸奸之徒自作不靖。以诖误国事。珥岂是树党之人哉。珥前后疏章及行事立论。今俱在焉。使有一毫如论者之言。臣等当伏诬罔之诛矣。今之论者于成浑。尤加侮蔑。至谓学问醇杂。有不足言。夫学问醇杂。固非此辈之所敢知也。浑之学。得之家庭。渊源甚正。庄重纯粹。表里如一。德器成就。望之嶷然。李珥所尝敬叹。以谓操履敦确。吾所不及者也。顾以浑在世寿考。屡经党祸。故为群小所媢嫉特甚。其所搆捏罗织。无所不至。如今所谓遗 君主和杀士之目。是也。夫浑本一处士。虽尝屡赴 召命。而在朝不过数月。其进退之间。处义甚严。皆可以为法。当倭变之作。人臣之义。固当奔赴 阙下。执羁靮以从。然浑方退处田野。 召命不及。其义亦未可自进。夫守道自重者。与出身事君者不同。国恤入赴。臣子之常节。然司马光当神宗丧。不召自入。程子当高后丧。召而不赴。我 仁顺仁圣之丧。李珥皆自外入赴。而
于平。其用心公平正大。至诚恻怛。真可以挽回世道。而不幸忮害轻躁之人出于其间。不求其心而遽疑其迹。东西交攻。蛮触不已。卒之许篈,应溉之疏出而遂不可收拾矣。此乃憸奸之徒自作不靖。以诖误国事。珥岂是树党之人哉。珥前后疏章及行事立论。今俱在焉。使有一毫如论者之言。臣等当伏诬罔之诛矣。今之论者于成浑。尤加侮蔑。至谓学问醇杂。有不足言。夫学问醇杂。固非此辈之所敢知也。浑之学。得之家庭。渊源甚正。庄重纯粹。表里如一。德器成就。望之嶷然。李珥所尝敬叹。以谓操履敦确。吾所不及者也。顾以浑在世寿考。屡经党祸。故为群小所媢嫉特甚。其所搆捏罗织。无所不至。如今所谓遗 君主和杀士之目。是也。夫浑本一处士。虽尝屡赴 召命。而在朝不过数月。其进退之间。处义甚严。皆可以为法。当倭变之作。人臣之义。固当奔赴 阙下。执羁靮以从。然浑方退处田野。 召命不及。其义亦未可自进。夫守道自重者。与出身事君者不同。国恤入赴。臣子之常节。然司马光当神宗丧。不召自入。程子当高后丧。召而不赴。我 仁顺仁圣之丧。李珥皆自外入赴。而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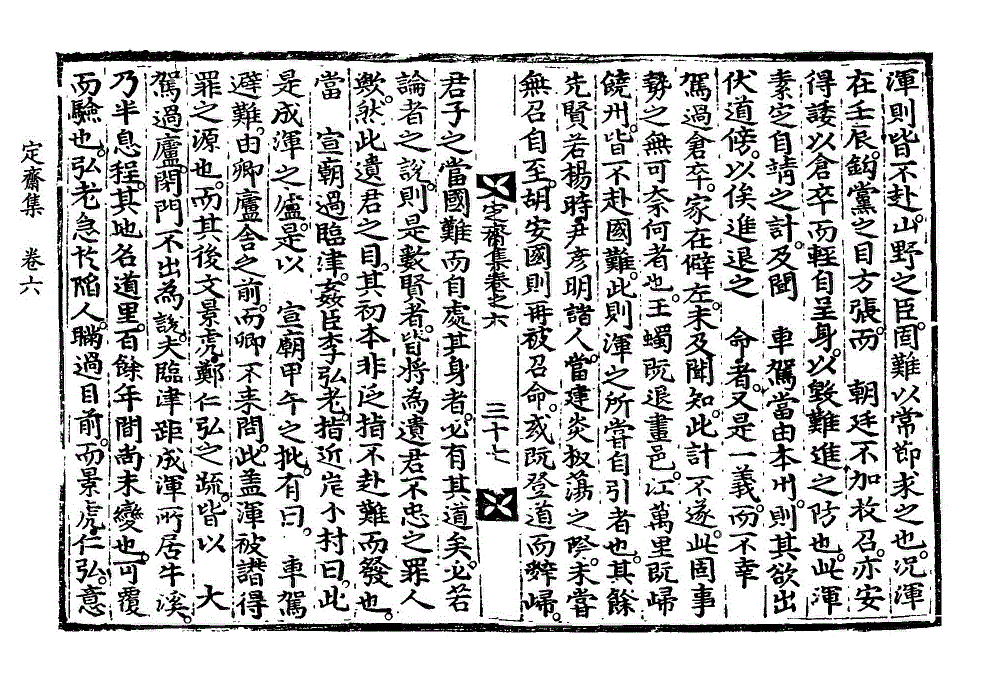 浑则皆不赴。山野之臣。固难以常节求之也。况浑在壬辰。钩党之目方张。而 朝廷不加收召。亦安得诿以仓卒而轻自呈身。以毁难进之防也。此浑素定自靖之计。及闻 车驾当由本州。则其欲出伏道傍。以俟进退之 命者。又是一义。而不幸 驾过仓卒。家在僻左。未及闻知。此计不遂。此固事势之无可奈何者也。王蠋既退昼邑。江万里既归饶州。皆不赴国难。此则浑之所尝自引者也。其馀先贤若杨时,尹彦明诸人。当建炎板荡之际。未尝无召自至。胡安国则再被召命。或既登道而辞归。君子之当国难而自处其身者。必有其道矣。必若论者之说。则是数贤者。皆将为遗君不忠之罪人欤。然此遗君之目。其初本非泛指不赴难而发也。当 宣庙过临津。奸臣李弘老。指近岸小村曰。此是成浑之庐。是以 宣庙甲午之批。有曰。 车驾避难。由卿庐舍之前。而卿不来问。此盖浑被谮得罪之源也。而其后文景虎,郑仁弘之疏。皆以 大驾过庐。闭门不出为说。夫临津距成浑所居牛溪。乃半息程。其地名道里。百馀年间尚未变也。可覆而验也。弘老急于陷人。瞒过目前。而景虎,仁弘。意
浑则皆不赴。山野之臣。固难以常节求之也。况浑在壬辰。钩党之目方张。而 朝廷不加收召。亦安得诿以仓卒而轻自呈身。以毁难进之防也。此浑素定自靖之计。及闻 车驾当由本州。则其欲出伏道傍。以俟进退之 命者。又是一义。而不幸 驾过仓卒。家在僻左。未及闻知。此计不遂。此固事势之无可奈何者也。王蠋既退昼邑。江万里既归饶州。皆不赴国难。此则浑之所尝自引者也。其馀先贤若杨时,尹彦明诸人。当建炎板荡之际。未尝无召自至。胡安国则再被召命。或既登道而辞归。君子之当国难而自处其身者。必有其道矣。必若论者之说。则是数贤者。皆将为遗君不忠之罪人欤。然此遗君之目。其初本非泛指不赴难而发也。当 宣庙过临津。奸臣李弘老。指近岸小村曰。此是成浑之庐。是以 宣庙甲午之批。有曰。 车驾避难。由卿庐舍之前。而卿不来问。此盖浑被谮得罪之源也。而其后文景虎,郑仁弘之疏。皆以 大驾过庐。闭门不出为说。夫临津距成浑所居牛溪。乃半息程。其地名道里。百馀年间尚未变也。可覆而验也。弘老急于陷人。瞒过目前。而景虎,仁弘。意定斋集卷之六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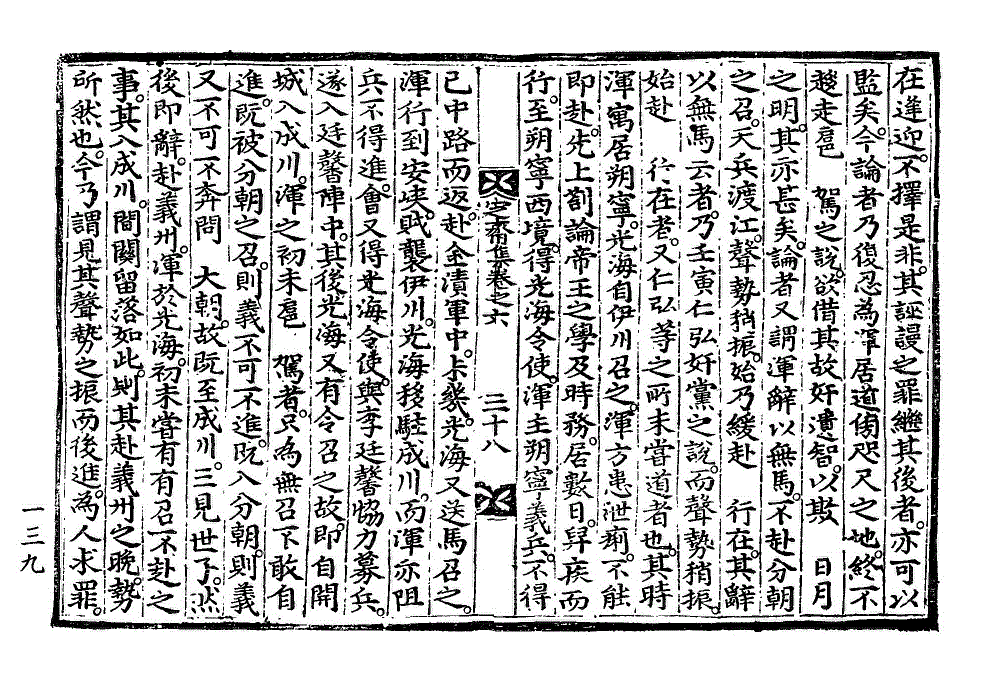 在逢迎。不择是非。其诬谩之罪继其后者。亦可以监矣。今论者乃复忍为浑居道傍咫尺之地。终不趍走扈 驾之说。欲借其故奸遗智。以欺 日月之明。其亦甚矣。论者又谓浑辞以无马。不赴分朝之召。天兵渡江。声势稍振。始乃缓赴 行在。其辞以无马云者。乃壬寅仁弘奸党之说。而声势稍振。始赴 行在者。又仁弘等之所未尝道者也。其时浑寓居朔宁。光海自伊川召之。浑方患泄痢。不能即赴。先上劄论帝王之学及时务。居数日。舁疾而行。至朔宁西境。得光海令使。浑主朔宁义兵。不得已中路而返。赴金渍军中。未几。光海又送马召之。浑行到安峡。贼袭伊川。光海移驻成川。而浑亦阻兵不得进。会又得光海令使。与李廷馨协力募兵。遂入廷馨阵中。其后光海又有令召之故。即自开城入成川。浑之初未扈 驾者。只为无召不敢自进。既被分朝之召。则义不可不进。既入分朝。则义又不可不奔问 大朝。故既至成川。三见世子。然后即辞。赴义州。浑于光海。初未尝有有召不赴之事。其入成川。间关留落如此。则其赴义州之晚。势所然也。今乃谓见其声势之振而后进。为人求罪。
在逢迎。不择是非。其诬谩之罪继其后者。亦可以监矣。今论者乃复忍为浑居道傍咫尺之地。终不趍走扈 驾之说。欲借其故奸遗智。以欺 日月之明。其亦甚矣。论者又谓浑辞以无马。不赴分朝之召。天兵渡江。声势稍振。始乃缓赴 行在。其辞以无马云者。乃壬寅仁弘奸党之说。而声势稍振。始赴 行在者。又仁弘等之所未尝道者也。其时浑寓居朔宁。光海自伊川召之。浑方患泄痢。不能即赴。先上劄论帝王之学及时务。居数日。舁疾而行。至朔宁西境。得光海令使。浑主朔宁义兵。不得已中路而返。赴金渍军中。未几。光海又送马召之。浑行到安峡。贼袭伊川。光海移驻成川。而浑亦阻兵不得进。会又得光海令使。与李廷馨协力募兵。遂入廷馨阵中。其后光海又有令召之故。即自开城入成川。浑之初未扈 驾者。只为无召不敢自进。既被分朝之召。则义不可不进。既入分朝。则义又不可不奔问 大朝。故既至成川。三见世子。然后即辞。赴义州。浑于光海。初未尝有有召不赴之事。其入成川。间关留落如此。则其赴义州之晚。势所然也。今乃谓见其声势之振而后进。为人求罪。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0H 页
 一至于此。其亦巧且惨矣。当癸巳甲午之间。天将宿兵连年战不时决。有许款退倭之议。侍郎顾养谦遣参将移咨曰。吾请受贼降 朝廷。以尔国曾告东征将士之罪。以此吾将得罪。受降又不成矣。尔国今将贼势与尔国危急之实。备细奏闻。则 朝廷必信。受降之事成矣。尔国得纾危急。因以闲暇治农训兵。以报大雠。于义何害。领相柳成龙上劄。请从顾指。 上可之。方议奏闻。难其辞命。备局合议。浑以为今既不免胁持上本。则当言顾公劄付。深得情实。送贼归巢。以宽危急。为后日复雠之地。亦 皇恩也云云。则我 国复雠之义。初无愧屈。而 天朝将相。稍解愠怒。亦有向后拯救之望。求之大义。亦无所害矣。此今之论者所谓和议者也。今论当时事势。我 国之不能有所树立。自剪此贼。则已决矣。使天兵奋威力战。荡覆巢穴。以讫天诛。则岂不善之善哉。然而 皇敕既使朝鲜自为计。而无再举之意。在东诸将。又皆力屈粮竭。不能制敌。只思许倭纳款。此则权不在我。又非我之所可如何也。夫谓倭奴为万世必报之雠者。自系我 国之义。在 天朝则绥纳要荒。自是古事。劳
一至于此。其亦巧且惨矣。当癸巳甲午之间。天将宿兵连年战不时决。有许款退倭之议。侍郎顾养谦遣参将移咨曰。吾请受贼降 朝廷。以尔国曾告东征将士之罪。以此吾将得罪。受降又不成矣。尔国今将贼势与尔国危急之实。备细奏闻。则 朝廷必信。受降之事成矣。尔国得纾危急。因以闲暇治农训兵。以报大雠。于义何害。领相柳成龙上劄。请从顾指。 上可之。方议奏闻。难其辞命。备局合议。浑以为今既不免胁持上本。则当言顾公劄付。深得情实。送贼归巢。以宽危急。为后日复雠之地。亦 皇恩也云云。则我 国复雠之义。初无愧屈。而 天朝将相。稍解愠怒。亦有向后拯救之望。求之大义。亦无所害矣。此今之论者所谓和议者也。今论当时事势。我 国之不能有所树立。自剪此贼。则已决矣。使天兵奋威力战。荡覆巢穴。以讫天诛。则岂不善之善哉。然而 皇敕既使朝鲜自为计。而无再举之意。在东诸将。又皆力屈粮竭。不能制敌。只思许倭纳款。此则权不在我。又非我之所可如何也。夫谓倭奴为万世必报之雠者。自系我 国之义。在 天朝则绥纳要荒。自是古事。劳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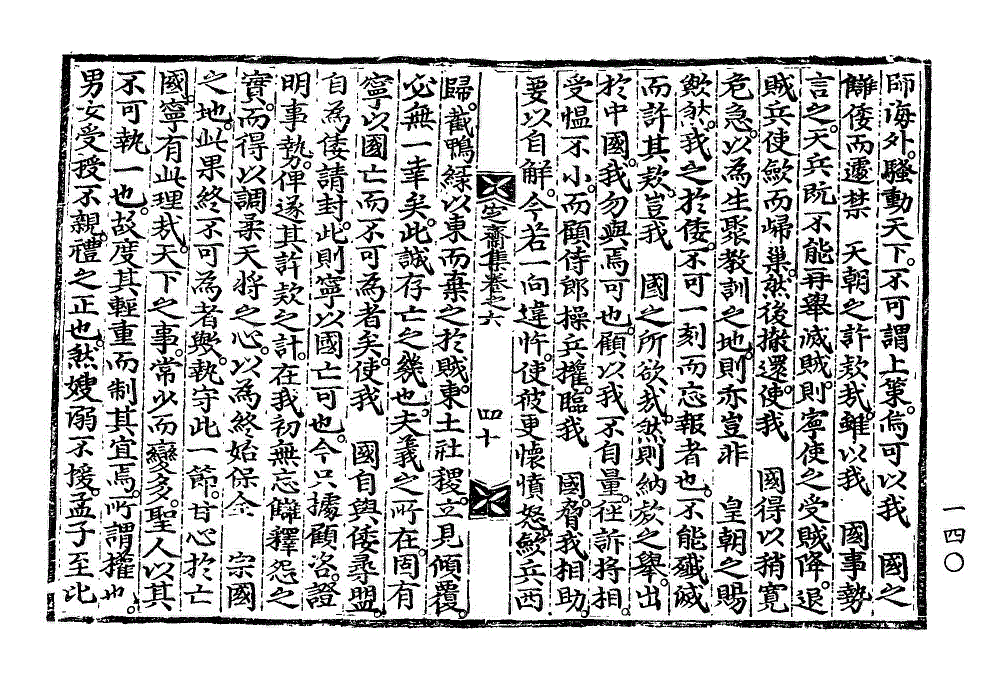 师海外。骚动天下。不可谓上策。乌可以我 国之雠倭而遽禁 天朝之许款哉。虽以我 国事势言之。天兵既不能再举灭贼。则宁使之受贼降。退贼兵使敛而归巢。然后撤还。使我 国得以稍宽危急。以为生聚教训之地。则亦岂非 皇朝之赐欤然。我之于倭。不可一刻而忘报者也。不能歼灭而许其款。岂我 国之所欲哉。然则纳款之举。出于中国。我勿与焉可也。顾以我不自量。径诉将相。受愠不小。而顾侍郎操兵权。临我 国。胁我相助。要以自解。今若一向违忤。使彼更怀愤怒。敛兵西归。截鸭绿以东而弃之于贼。东土社稷。立见倾覆。必无一幸矣。此诚存亡之几也。夫义之所在。固有宁以国亡而不可为者矣。使我 国自与倭寻盟。自为倭请封。此则宁以国亡可也。今只据顾咨。證明事势。俾遂其许款之计。在我初无忘雠释怨之实。而得以调柔天将之心。以为终始保全 宗国之地。此果终不可为者欤。执守此一节。甘心于亡国。宁有此理哉。天下之事。常少而变多。圣人以其不可执一也。故度其轻重而制其宜焉。所谓权也。男女受授不亲。礼之正也。然嫂溺不援。孟子至比
师海外。骚动天下。不可谓上策。乌可以我 国之雠倭而遽禁 天朝之许款哉。虽以我 国事势言之。天兵既不能再举灭贼。则宁使之受贼降。退贼兵使敛而归巢。然后撤还。使我 国得以稍宽危急。以为生聚教训之地。则亦岂非 皇朝之赐欤然。我之于倭。不可一刻而忘报者也。不能歼灭而许其款。岂我 国之所欲哉。然则纳款之举。出于中国。我勿与焉可也。顾以我不自量。径诉将相。受愠不小。而顾侍郎操兵权。临我 国。胁我相助。要以自解。今若一向违忤。使彼更怀愤怒。敛兵西归。截鸭绿以东而弃之于贼。东土社稷。立见倾覆。必无一幸矣。此诚存亡之几也。夫义之所在。固有宁以国亡而不可为者矣。使我 国自与倭寻盟。自为倭请封。此则宁以国亡可也。今只据顾咨。證明事势。俾遂其许款之计。在我初无忘雠释怨之实。而得以调柔天将之心。以为终始保全 宗国之地。此果终不可为者欤。执守此一节。甘心于亡国。宁有此理哉。天下之事。常少而变多。圣人以其不可执一也。故度其轻重而制其宜焉。所谓权也。男女受授不亲。礼之正也。然嫂溺不援。孟子至比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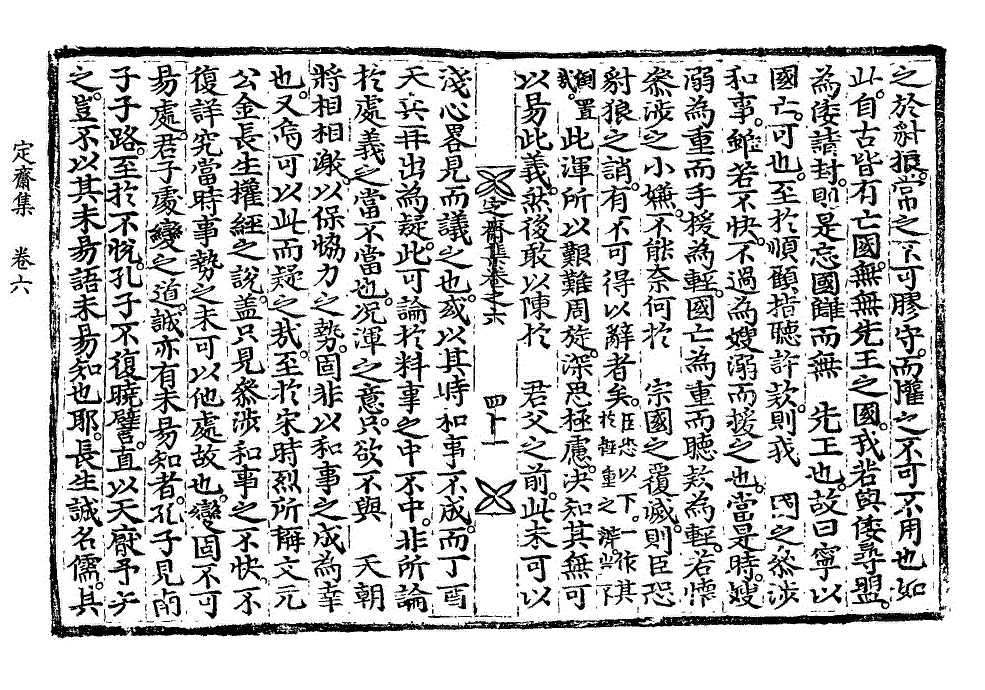 之于豺狼。常之不可胶守。而权之不可不用也如此。自古皆有亡国。无无先王之国。我若与倭寻盟。为倭请封。则是忘国雠而无 先王也。故曰宁以国亡。可也。至于顺顾指听许款。则我 国之参涉和事。虽若不快。不过为嫂溺而援之也。当是时。嫂溺为重而手援为轻。国亡为重而听款为轻。若怀参涉之小嫌。不能奈何于 宗国之覆灭。则臣恐豺狼之诮。有不可得以辞者矣。(臣恐以下。一作其于轻重之辨。岂不倒置哉。)此浑所以艰难周旋。深思极虑。决知其无可以易此义。然后敢以陈于 君父之前。此未可以浅心略见而议之也。或以其时和事不成。而丁酉天兵再出为疑。此可论于料事之中不中。非所论于处义之当不当也。况浑之意。只欲不与 天朝将相相激。以保协力之势。固非以和事之成为幸也。又乌可以此而疑之哉。至于宋时烈所称文元公金长生权经之说。盖只见参涉和事之不快。不复详究当时事势之未可以他处故也。变固不可易处。君子处变之道。诚亦有未易知者。孔子见南子。子路至于不悦。孔子不复晓譬。直以天厌予矢之。岂不以其未易语未易知也耶。长生诚名儒。其
之于豺狼。常之不可胶守。而权之不可不用也如此。自古皆有亡国。无无先王之国。我若与倭寻盟。为倭请封。则是忘国雠而无 先王也。故曰宁以国亡。可也。至于顺顾指听许款。则我 国之参涉和事。虽若不快。不过为嫂溺而援之也。当是时。嫂溺为重而手援为轻。国亡为重而听款为轻。若怀参涉之小嫌。不能奈何于 宗国之覆灭。则臣恐豺狼之诮。有不可得以辞者矣。(臣恐以下。一作其于轻重之辨。岂不倒置哉。)此浑所以艰难周旋。深思极虑。决知其无可以易此义。然后敢以陈于 君父之前。此未可以浅心略见而议之也。或以其时和事不成。而丁酉天兵再出为疑。此可论于料事之中不中。非所论于处义之当不当也。况浑之意。只欲不与 天朝将相相激。以保协力之势。固非以和事之成为幸也。又乌可以此而疑之哉。至于宋时烈所称文元公金长生权经之说。盖只见参涉和事之不快。不复详究当时事势之未可以他处故也。变固不可易处。君子处变之道。诚亦有未易知者。孔子见南子。子路至于不悦。孔子不复晓譬。直以天厌予矢之。岂不以其未易语未易知也耶。长生诚名儒。其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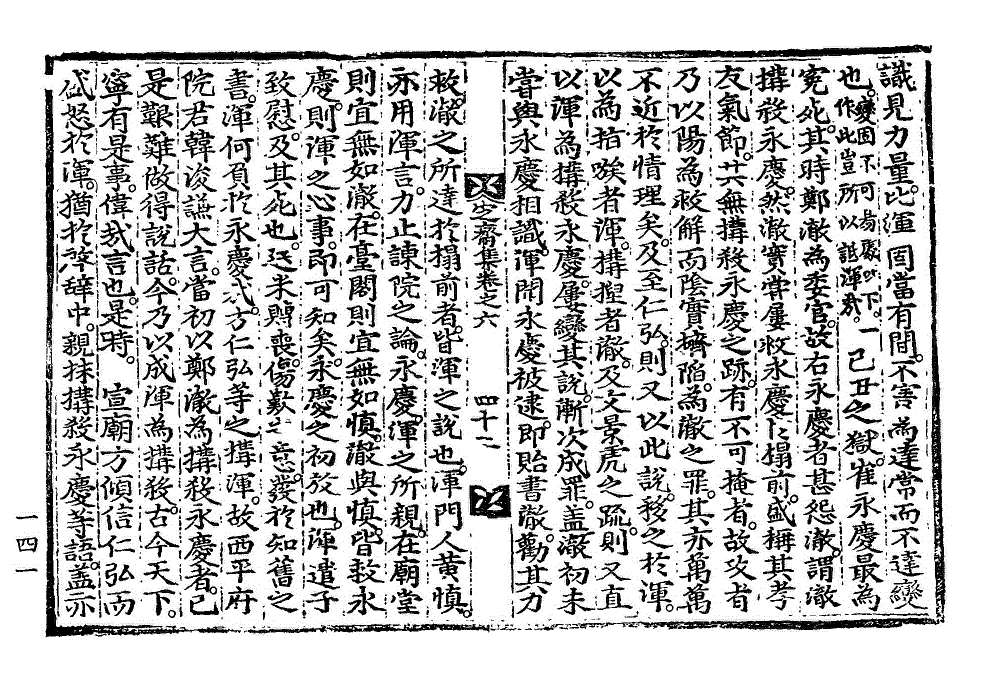 识见力量。比浑固当有间。不害为达常而不达变也。(变固不可易处以下。一作此岂所以诋浑哉。)己丑之狱。崔永庆最为冤死。其时郑澈为委官。故右永庆者甚怨澈。谓澈搆杀永庆。然澈实尝屡救永庆于榻前。盛称其孝友气节。其无搆杀永庆之迹。有不可掩者。故攻者乃以阳为救解而阴实挤陷。为澈之罪。其亦万万不近于情理矣。及至仁弘。则又以此说。移之于浑。以为指嗾者浑。搆捏者澈。及文景虎之疏。则又直以浑为搆杀永庆。屡变其说。渐次成罪。盖澈初未尝与永庆相识。浑闻永庆被逮。即贻书澈。劝其力救。澈之所达于榻前者。皆浑之说也。浑门人黄慎。亦用浑言。力止谏院之论。永庆。浑之所亲。在庙堂则宜无如澈。在台阁则宜无如慎。澈与慎。皆救永庆。则浑之心事。即可知矣。永庆之初放也。浑遣子致慰。及其死也。送米赙丧。伤叹之意。发于知旧之书。浑何负于永庆哉。方仁弘等之搆浑。故西平府院君韩浚谦大言。当初以郑澈为搆杀永庆者。已是艰难做得说话。今乃以成浑为搆杀。古今天下。宁有是事。伟哉言也。是时。 宣庙方倾信仁弘而盛怒于浑。犹于启辞中。亲抹搆杀永庆等语。盖亦
识见力量。比浑固当有间。不害为达常而不达变也。(变固不可易处以下。一作此岂所以诋浑哉。)己丑之狱。崔永庆最为冤死。其时郑澈为委官。故右永庆者甚怨澈。谓澈搆杀永庆。然澈实尝屡救永庆于榻前。盛称其孝友气节。其无搆杀永庆之迹。有不可掩者。故攻者乃以阳为救解而阴实挤陷。为澈之罪。其亦万万不近于情理矣。及至仁弘。则又以此说。移之于浑。以为指嗾者浑。搆捏者澈。及文景虎之疏。则又直以浑为搆杀永庆。屡变其说。渐次成罪。盖澈初未尝与永庆相识。浑闻永庆被逮。即贻书澈。劝其力救。澈之所达于榻前者。皆浑之说也。浑门人黄慎。亦用浑言。力止谏院之论。永庆。浑之所亲。在庙堂则宜无如澈。在台阁则宜无如慎。澈与慎。皆救永庆。则浑之心事。即可知矣。永庆之初放也。浑遣子致慰。及其死也。送米赙丧。伤叹之意。发于知旧之书。浑何负于永庆哉。方仁弘等之搆浑。故西平府院君韩浚谦大言。当初以郑澈为搆杀永庆者。已是艰难做得说话。今乃以成浑为搆杀。古今天下。宁有是事。伟哉言也。是时。 宣庙方倾信仁弘而盛怒于浑。犹于启辞中。亲抹搆杀永庆等语。盖亦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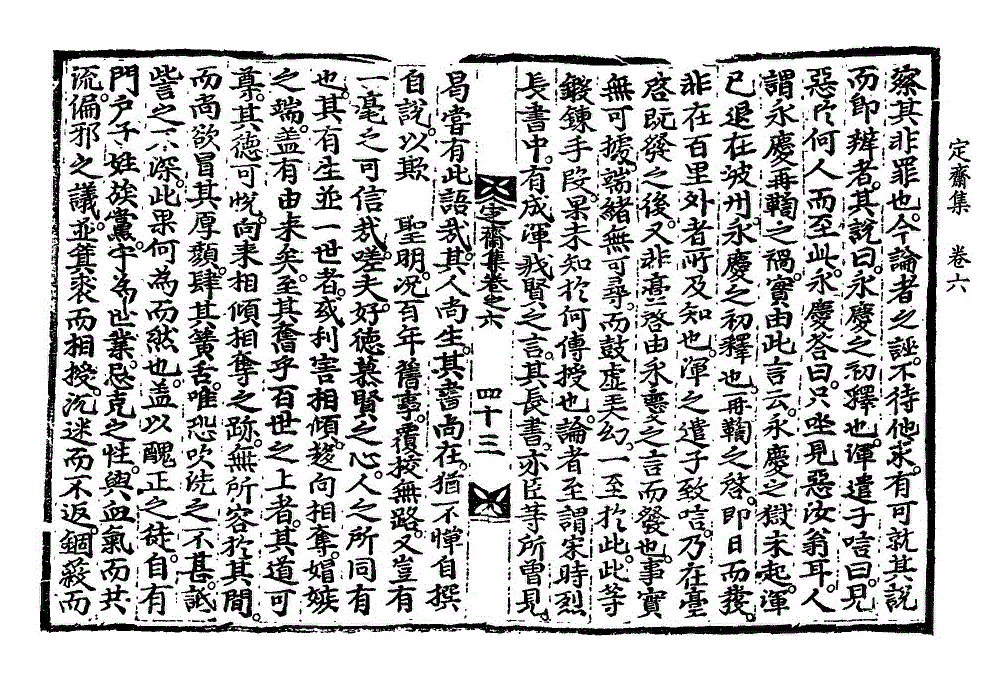 察其非罪也。今论者之诬。不待他求。有可就其说而即辨者。其说曰。永庆之初释也。浑遣子唁曰。见恶于何人而至此。永庆答曰。只坐见恶汝翁耳。人谓永庆再鞫之祸。实由此言云。永庆之狱未起。浑已退在坡州。永庆之初释也。再鞫之启。即日而发。非在百里外者所及知也。浑之遣子致唁。乃在台启既发之后。又非台启由永庆之言而发也。事实无可据。端绪无可寻。而鼓虚弄幻。一至于此。此等锻鍊手段。果未知于何传授也。论者至谓宋时烈长书中。有成浑戕贤之言。其长书。亦臣等所曾见。曷尝有此语哉。其人尚生。其书尚在。犹不惮自撰自说。以欺 圣明。况百年旧事。覆校无路。又岂有一毫之可信哉。嗟夫。好德慕贤之心。人之所同有也。其有生并一世者。或利害相倾。趍向相夺。媢嫉之端。盖有由来矣。至其奋乎百世之上者。其道可尊。其德可悦。向来相倾相夺之迹。无所容于其间。而尚欲冒其厚颜。肆其簧舌。唯恐吹洗之不甚。诋訾之不深。此果何为而然也。盖以丑正之徒。自有门户子姓族党。守为世业。忌克之性。与血气而共流。偏邪之议。并箕裘而相授。沉迷而不返。锢蔽而
察其非罪也。今论者之诬。不待他求。有可就其说而即辨者。其说曰。永庆之初释也。浑遣子唁曰。见恶于何人而至此。永庆答曰。只坐见恶汝翁耳。人谓永庆再鞫之祸。实由此言云。永庆之狱未起。浑已退在坡州。永庆之初释也。再鞫之启。即日而发。非在百里外者所及知也。浑之遣子致唁。乃在台启既发之后。又非台启由永庆之言而发也。事实无可据。端绪无可寻。而鼓虚弄幻。一至于此。此等锻鍊手段。果未知于何传授也。论者至谓宋时烈长书中。有成浑戕贤之言。其长书。亦臣等所曾见。曷尝有此语哉。其人尚生。其书尚在。犹不惮自撰自说。以欺 圣明。况百年旧事。覆校无路。又岂有一毫之可信哉。嗟夫。好德慕贤之心。人之所同有也。其有生并一世者。或利害相倾。趍向相夺。媢嫉之端。盖有由来矣。至其奋乎百世之上者。其道可尊。其德可悦。向来相倾相夺之迹。无所容于其间。而尚欲冒其厚颜。肆其簧舌。唯恐吹洗之不甚。诋訾之不深。此果何为而然也。盖以丑正之徒。自有门户子姓族党。守为世业。忌克之性。与血气而共流。偏邪之议。并箕裘而相授。沉迷而不返。锢蔽而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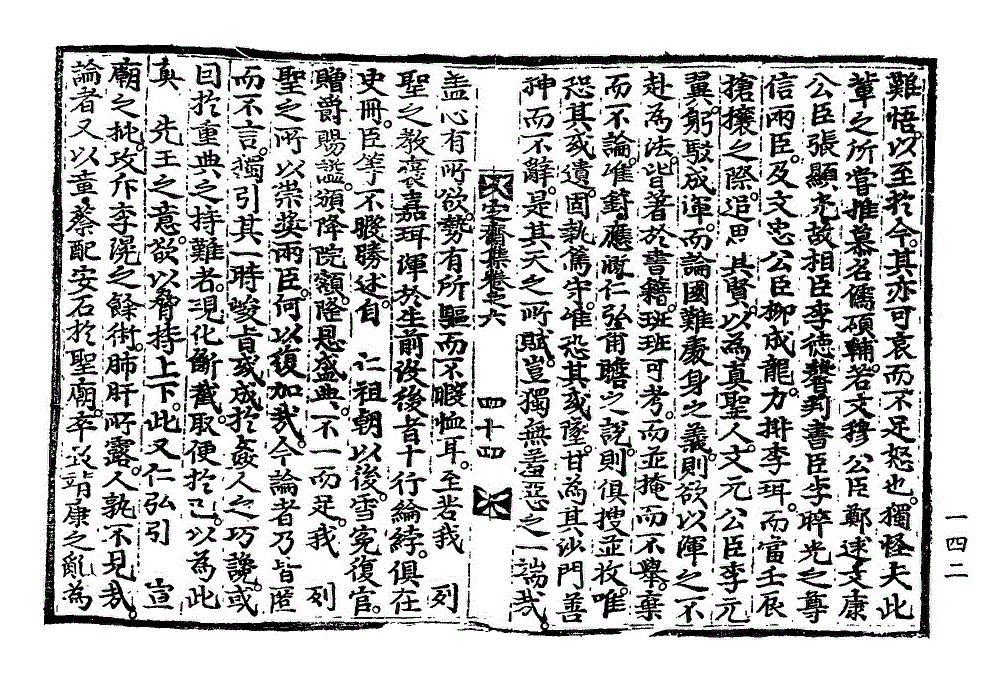 难悟。以至于今。其亦可哀而不足怒也。独怪夫此辈之所尝推慕名儒硕辅。若文穆公臣郑逑,文康公臣张显光,故相臣李德馨,判书臣李晬光之尊信两臣。及文忠公臣柳成龙。力排李珥。而当壬辰抢攘之际。追思其贤。以为真圣人。文元公臣李元翼。躬驳成浑。而论国难处身之义。则欲以浑之不赴为法。皆著于书籍。班班可考。而并掩而不举。弃而不论。唯篈,应溉,仁弘,尔瞻之说。则俱搜并收。唯恐其或遗。固执笃守。唯恐其或坠。甘为其沙门善神而不辞。是其天之所赋。岂独无羞恶之一端哉。盖心有所欲。势有所驱而不暇恤耳。至若我 列圣之教褒嘉珥浑于生前没后者十行纶綍。俱在史册。臣等不暇胜述。自 仁祖朝以后。雪冤复官。赠爵赐谥。颁降院额。隆恩盛典。不一而足。我 列圣之所以崇奖两臣。何以复加哉。今论者乃皆匿而不言。独引其一时峻旨或成于奸人之巧谗。或因于重典之持难者。现化断截。取便于己。以为此真 先王之意。欲以胁持上下。此又仁弘引 宣庙之批。攻斥李滉之馀术。肺肝所露。人孰不见哉。论者又以章,蔡配安石于圣庙。卒致靖康之乱为
难悟。以至于今。其亦可哀而不足怒也。独怪夫此辈之所尝推慕名儒硕辅。若文穆公臣郑逑,文康公臣张显光,故相臣李德馨,判书臣李晬光之尊信两臣。及文忠公臣柳成龙。力排李珥。而当壬辰抢攘之际。追思其贤。以为真圣人。文元公臣李元翼。躬驳成浑。而论国难处身之义。则欲以浑之不赴为法。皆著于书籍。班班可考。而并掩而不举。弃而不论。唯篈,应溉,仁弘,尔瞻之说。则俱搜并收。唯恐其或遗。固执笃守。唯恐其或坠。甘为其沙门善神而不辞。是其天之所赋。岂独无羞恶之一端哉。盖心有所欲。势有所驱而不暇恤耳。至若我 列圣之教褒嘉珥浑于生前没后者十行纶綍。俱在史册。臣等不暇胜述。自 仁祖朝以后。雪冤复官。赠爵赐谥。颁降院额。隆恩盛典。不一而足。我 列圣之所以崇奖两臣。何以复加哉。今论者乃皆匿而不言。独引其一时峻旨或成于奸人之巧谗。或因于重典之持难者。现化断截。取便于己。以为此真 先王之意。欲以胁持上下。此又仁弘引 宣庙之批。攻斥李滉之馀术。肺肝所露。人孰不见哉。论者又以章,蔡配安石于圣庙。卒致靖康之乱为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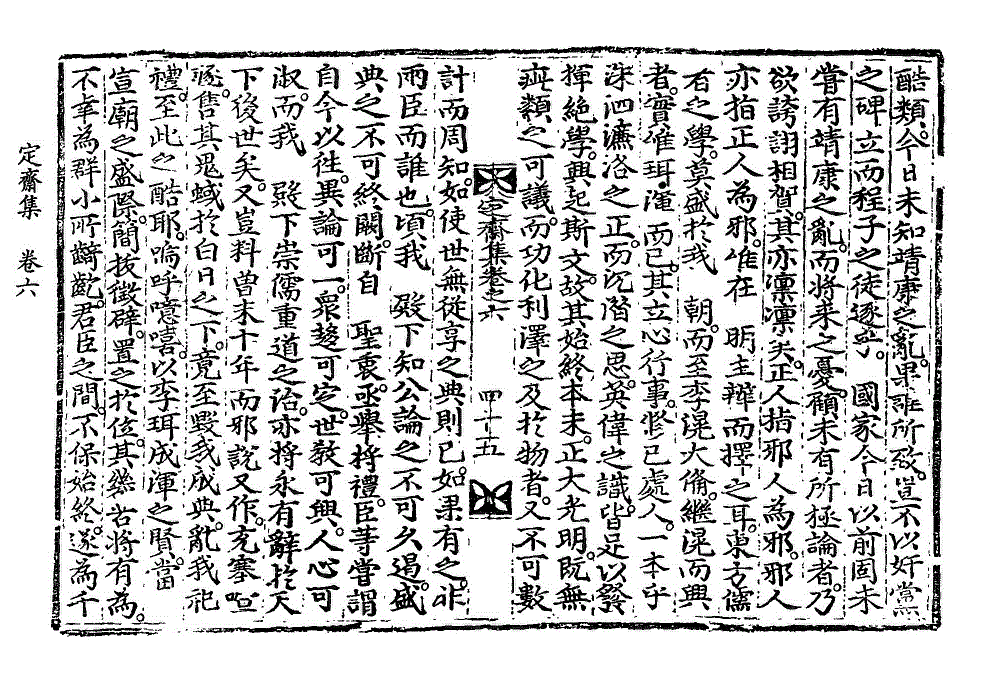 酷类。今日未知靖康之乱。果谁所致。岂不以奸党之碑立而程子之徒逐乎。 国家今日以前固未尝有靖康之乱。而将来之忧。顾未有所极论者。乃欲誇诩相贺。其亦凛凛矣。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唯在 明主辨而择之耳。东方儒者之学。莫盛于我 朝。而至李滉大备。继滉而兴者。实唯珥,浑而已。其立心行事。修己处人。一本乎洙泗濂洛之正。而沉潜之思。英伟之识。皆足以发挥绝学。兴起斯文。故其始终本末。正大光明。既无疵颣之可议。而功化利泽之及于物者。又不可数计而周知。如使世无从享之典则已。如果有之。非两臣而谁也。顷我 殿下知公论之不可久遏。盛典之不可终阙。断自 圣衷。亟举将礼。臣等尝谓自今以往。异论可一。众趍可定。世教可兴。人心可淑。而我 殿下崇儒重道之治。亦将永有辞于天下后世矣。又岂料曾未十年而邪说又作。充塞喧豗。售其鬼蜮于白日之下。竟至毁我成典。乱我祀礼。至此之酷耶。呜呼噫嘻。以李珥成浑之贤。当 宣庙之盛际。简拔徵辟。置之于位。其几若将有为。不幸为群小所齮龁。君臣之间。不保始终。遂为千
酷类。今日未知靖康之乱。果谁所致。岂不以奸党之碑立而程子之徒逐乎。 国家今日以前固未尝有靖康之乱。而将来之忧。顾未有所极论者。乃欲誇诩相贺。其亦凛凛矣。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唯在 明主辨而择之耳。东方儒者之学。莫盛于我 朝。而至李滉大备。继滉而兴者。实唯珥,浑而已。其立心行事。修己处人。一本乎洙泗濂洛之正。而沉潜之思。英伟之识。皆足以发挥绝学。兴起斯文。故其始终本末。正大光明。既无疵颣之可议。而功化利泽之及于物者。又不可数计而周知。如使世无从享之典则已。如果有之。非两臣而谁也。顷我 殿下知公论之不可久遏。盛典之不可终阙。断自 圣衷。亟举将礼。臣等尝谓自今以往。异论可一。众趍可定。世教可兴。人心可淑。而我 殿下崇儒重道之治。亦将永有辞于天下后世矣。又岂料曾未十年而邪说又作。充塞喧豗。售其鬼蜮于白日之下。竟至毁我成典。乱我祀礼。至此之酷耶。呜呼噫嘻。以李珥成浑之贤。当 宣庙之盛际。简拔徵辟。置之于位。其几若将有为。不幸为群小所齮龁。君臣之间。不保始终。遂为千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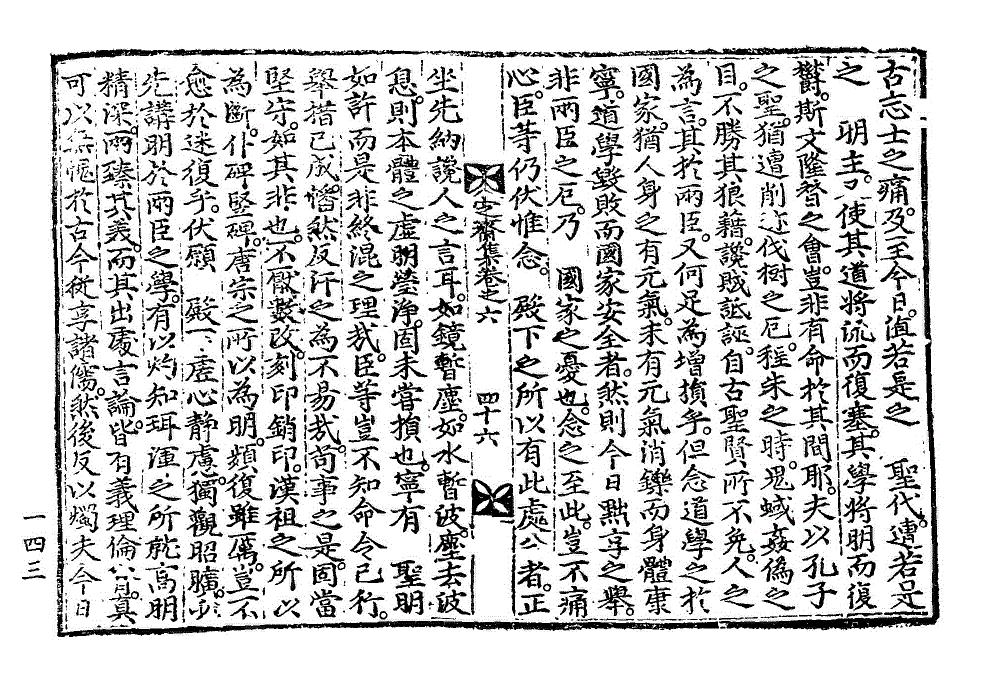 古志士之痛。及至今日。值若是之 圣代。遭若是之 明主。又使其道将流而复塞。其学将明而复郁。斯文隆替之会。岂非有命于其间耶。夫以孔子之圣。犹遭削迹伐树之厄。程朱之时。鬼蜮奸伪之目。不胜其狼藉。谗贼诋诬。自古圣贤所不免。人之为言。其于两臣。又何足为增损乎。但念道学之于国家。犹人身之有元气。未有元气消铄而身体康宁。道学毁败而国家安全者。然则今日黜享之举。非两臣之厄。乃 国家之忧也。念之至此。岂不痛心。臣等仍伏惟念。 殿下之所以有此处分者。正坐先纳谗人之言耳。如镜暂尘。如水暂波。尘去波息。则本体之虚明莹净。固未尝损也。宁有 圣明如许而是非终混之理哉。臣等岂不知命令已行。举措已成。幡然反汗之为不易哉。苟事之是。固当坚守。如其非也。不厌数改。刻印销印。汉祖之所以为断。仆碑竖碑。唐宗之所以为明。频复虽厉。岂不愈于迷复乎。伏愿 殿下虚心静虑。独观昭旷。必先讲明于两臣之学。有以灼知珥浑之所就高明精深。两臻其美。而其出处言论。皆有义理伦脊。真可以无愧于古今从享诸儒。然后反以烛夫今日
古志士之痛。及至今日。值若是之 圣代。遭若是之 明主。又使其道将流而复塞。其学将明而复郁。斯文隆替之会。岂非有命于其间耶。夫以孔子之圣。犹遭削迹伐树之厄。程朱之时。鬼蜮奸伪之目。不胜其狼藉。谗贼诋诬。自古圣贤所不免。人之为言。其于两臣。又何足为增损乎。但念道学之于国家。犹人身之有元气。未有元气消铄而身体康宁。道学毁败而国家安全者。然则今日黜享之举。非两臣之厄。乃 国家之忧也。念之至此。岂不痛心。臣等仍伏惟念。 殿下之所以有此处分者。正坐先纳谗人之言耳。如镜暂尘。如水暂波。尘去波息。则本体之虚明莹净。固未尝损也。宁有 圣明如许而是非终混之理哉。臣等岂不知命令已行。举措已成。幡然反汗之为不易哉。苟事之是。固当坚守。如其非也。不厌数改。刻印销印。汉祖之所以为断。仆碑竖碑。唐宗之所以为明。频复虽厉。岂不愈于迷复乎。伏愿 殿下虚心静虑。独观昭旷。必先讲明于两臣之学。有以灼知珥浑之所就高明精深。两臻其美。而其出处言论。皆有义理伦脊。真可以无愧于古今从享诸儒。然后反以烛夫今日定斋集卷之六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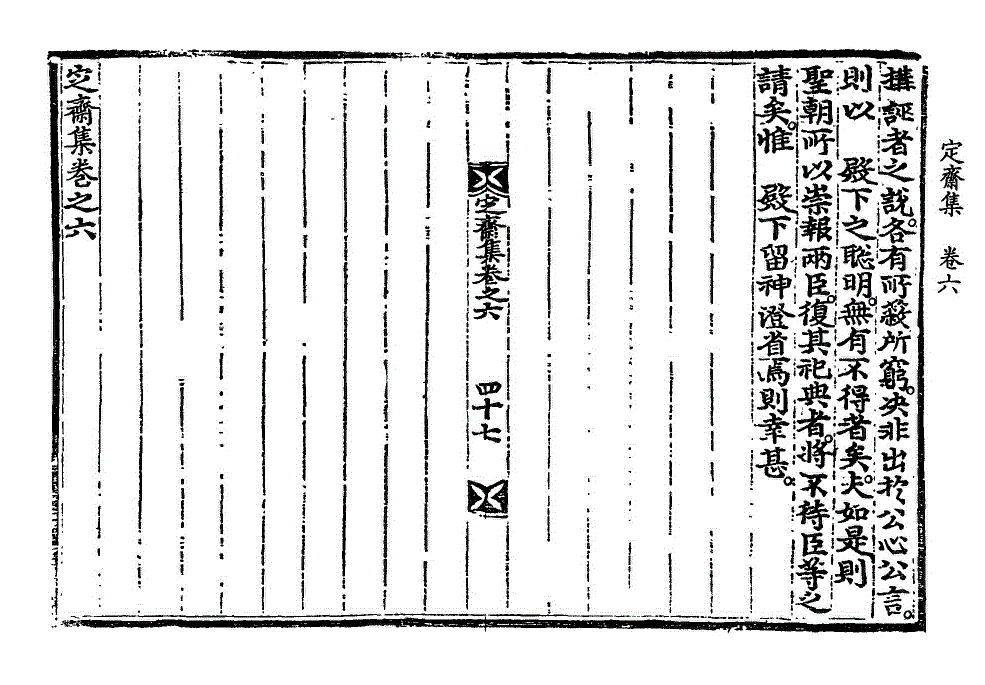 搆诬者之说。各有所蔽所穷。决非出于公心公言。则以 殿下之聪明。无有不得者矣。夫如是则 圣朝所以崇报两臣。复其祀典者。将不待臣等之请矣。惟 殿下留神澄省焉则幸甚。
搆诬者之说。各有所蔽所穷。决非出于公心公言。则以 殿下之聪明。无有不得者矣。夫如是则 圣朝所以崇报两臣。复其祀典者。将不待臣等之请矣。惟 殿下留神澄省焉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