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圃阴集卷之二 第 x 页
圃阴集卷之二(安东 金昌缉敬明 著)
书
书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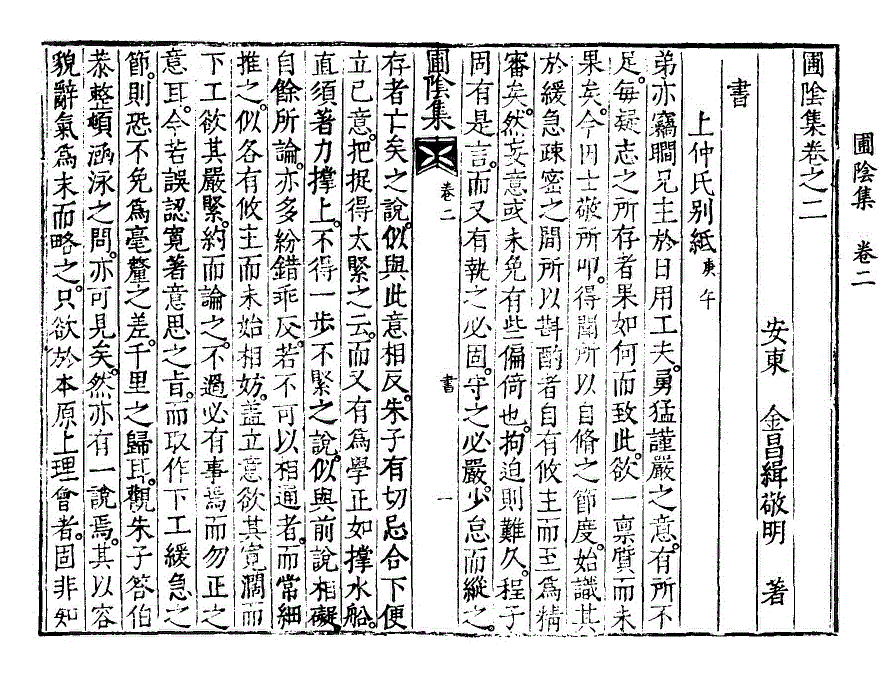 上仲氏别纸(庚午)
上仲氏别纸(庚午)弟亦窃瞷兄主于日用工夫。勇猛谨严之意。有所不足。每疑志之所存者果如何而致此。欲一禀质而未果矣。今因士敬所叩。得闻所以自脩之节度。始识其于缓急疏密之间所以斟酌者自有攸主而至为精审矣。然妄意或未免有些偏倚也。拘迫则难久。程子固有是言。而又有执之必固。守之必严。少怠而纵之。存者亡矣之说。似与此意相反。朱子有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之云。而又有为学正如撑水船。直须著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之说。似与前说相碍。自馀所论。亦多纷错乖反。若不可以相通者。而常细推之。似各有攸主而未始相妨。盖立意欲其宽阔而下工欲其严紧。约而论之。不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耳。今若误认宽著意思之旨。而取作下工缓急之节。则恐不免为毫釐之差。千里之归耳。观朱子答伯恭整顿涵泳之问。亦可见矣。然亦有一说焉。其以容貌辞气为末而略之。只欲于本原上理会者。固非知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4L 页
 道之言。只知规规于容貌辞气。而不知察此心之存否。则此又不知本末轻重之分者也。如此下工。恐难得力。朱子故曰。今之持敬者。皆妆点外事。故累坠不快活。不若直截于求放心上理会。此即程子所谓学要鞭辟近里。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之意也。此是老婆赤心真切说出者。若于此着力。则容貌辞气。自然不待安排。而不得不循规矩。所谓拘迫难久。亦不足为病矣。此其得力。实非徒屑屑于外者之比。窃谓兄主今日鞭后之道。尤在于此。伏望且试省却书册。工夫专一于此理会。如何如何。便甚遽。语不成伦。
道之言。只知规规于容貌辞气。而不知察此心之存否。则此又不知本末轻重之分者也。如此下工。恐难得力。朱子故曰。今之持敬者。皆妆点外事。故累坠不快活。不若直截于求放心上理会。此即程子所谓学要鞭辟近里。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之意也。此是老婆赤心真切说出者。若于此着力。则容貌辞气。自然不待安排。而不得不循规矩。所谓拘迫难久。亦不足为病矣。此其得力。实非徒屑屑于外者之比。窃谓兄主今日鞭后之道。尤在于此。伏望且试省却书册。工夫专一于此理会。如何如何。便甚遽。语不成伦。上仲氏(丁丑)
下示闵书。匆匆未暇谛视而槩之。虽费遁闪而难掩窘态矣。明德说。既曰兼心性则情自在其中。而不许其兼包者。是果何说耶。盖所谓心虽曰统性情。而若对性而言之。心则当以情为主。如曰明德不兼心性则已。岂有兼心而不兼情之理乎。匆遽未究其详。当俟后日之拜耳。
上仲氏
人气禀清明。而善情之发。十分纯一。不待充扩而自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5H 页
 无不善。则其意之随发者。亦必十分真实。不待禁止而自无不善。此乃心正则意必诚。而无待于诚之者也。气禀不能清明而不至于甚。则虽善情之发。不能十分纯一。须待充扩。而始无不善。而其意之随发者。则犹能十分真实。不待禁止而自无不善。此乃心虽不正。而意则犹诚。而亦无待于诚之者也。气禀不能清明之甚。则善情之发。既不能十分纯一。须待充扩而始无不善。而其意之随发者。又不能十分真实。而一欲充扩其善情。(即章句所谓知为善而去恶。)一不欲充扩其善情。(即章句所谓心之所发有未实。)于是乎意始有善有不善。而不可不加诚之之功也。若于此。禁止其不欲充扩善情之意。使欲充扩善情之意。十分真实。则意于是乎无不善。而即所谓诚之之功也。盖诚之之功。其所用力。只在于不欲充扩善情之意。而不在于欲充扩善情之意。以欲充扩善情之意。则乃自然而善无待于用力也。今道以谓缘情而运用者意也。而以恻隐之发而充扩。到十分尽者。为运用之善。则是以诚意而意无不善者为意之善也。以充扩有一分未足者。为运用之不善。则是以未诚意而意有善有不善者。为意之不善也。盖所谓意有善不善者。只就意不诚中。分别
无不善。则其意之随发者。亦必十分真实。不待禁止而自无不善。此乃心正则意必诚。而无待于诚之者也。气禀不能清明而不至于甚。则虽善情之发。不能十分纯一。须待充扩。而始无不善。而其意之随发者。则犹能十分真实。不待禁止而自无不善。此乃心虽不正。而意则犹诚。而亦无待于诚之者也。气禀不能清明之甚。则善情之发。既不能十分纯一。须待充扩而始无不善。而其意之随发者。又不能十分真实。而一欲充扩其善情。(即章句所谓知为善而去恶。)一不欲充扩其善情。(即章句所谓心之所发有未实。)于是乎意始有善有不善。而不可不加诚之之功也。若于此。禁止其不欲充扩善情之意。使欲充扩善情之意。十分真实。则意于是乎无不善。而即所谓诚之之功也。盖诚之之功。其所用力。只在于不欲充扩善情之意。而不在于欲充扩善情之意。以欲充扩善情之意。则乃自然而善无待于用力也。今道以谓缘情而运用者意也。而以恻隐之发而充扩。到十分尽者。为运用之善。则是以诚意而意无不善者为意之善也。以充扩有一分未足者。为运用之不善。则是以未诚意而意有善有不善者。为意之不善也。盖所谓意有善不善者。只就意不诚中。分别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5L 页
 其善不善。而今乃以意诚为善。意不诚为不善。固已失其本指矣。且道以之意。以充扩为明之之功。以到十分尽者。为诚之之功。故以诚之之功。为明之之中紧要处。是以明之诚之为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未知所谓充扩者。果何所指而言耶。以为指欲充扩善情之意而言。则是乃自然而善本无待于用力而明之也。以为指禁止其不欲充扩善情之意者而言。则是充扩。即为诚之之功。而其所谓充扩有一分未足。则不可不加诚之之功者。是为诚之之上。复有诚之之功矣。然则明之诚之之云。果将何以辨其浅深疏密之分乎。况云峰之说。以其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性发而为情。实其心之所发。心发而为意者观之。则其以明德与意。为两物也决矣。既以明德与意为两物。则便是以明之诚之为两事也。而今道以所论。则虽以明之诚之为有浅深疏密之分。而犹不判然以为两事。是虽曰解说云峰之说。而乃道以之说而非云峰之说也。道以之说。虽得。何救于云峰之失乎。至于所谓恻隐等情初无不善故因此明之者。则全述云峰之言。而似又直以明之之功。出之于诚之之外。而其指意尤未的确。有未易摸捉者。夫情既已无
其善不善。而今乃以意诚为善。意不诚为不善。固已失其本指矣。且道以之意。以充扩为明之之功。以到十分尽者。为诚之之功。故以诚之之功。为明之之中紧要处。是以明之诚之为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未知所谓充扩者。果何所指而言耶。以为指欲充扩善情之意而言。则是乃自然而善本无待于用力而明之也。以为指禁止其不欲充扩善情之意者而言。则是充扩。即为诚之之功。而其所谓充扩有一分未足。则不可不加诚之之功者。是为诚之之上。复有诚之之功矣。然则明之诚之之云。果将何以辨其浅深疏密之分乎。况云峰之说。以其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性发而为情。实其心之所发。心发而为意者观之。则其以明德与意。为两物也决矣。既以明德与意为两物。则便是以明之诚之为两事也。而今道以所论。则虽以明之诚之为有浅深疏密之分。而犹不判然以为两事。是虽曰解说云峰之说。而乃道以之说而非云峰之说也。道以之说。虽得。何救于云峰之失乎。至于所谓恻隐等情初无不善故因此明之者。则全述云峰之言。而似又直以明之之功。出之于诚之之外。而其指意尤未的确。有未易摸捉者。夫情既已无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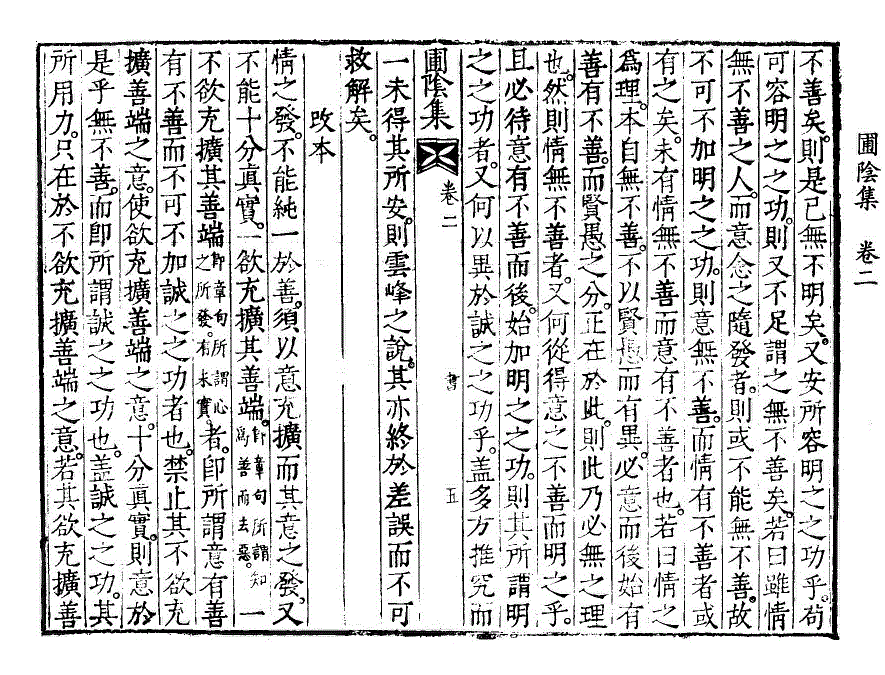 不善矣。则是已无不明矣。又安所容明之之功乎。苟可容明之之功。则又不足谓之无不善矣。若曰虽情无不善之人。而意念之随发者。则或不能无不善。故不可不加明之之功。则意无不善。而情有不善者或有之矣。未有情无不善而意有不善者也。若曰情之为理。本自无不善。不以贤愚而有异。必意而后始有善有不善。而贤愚之分。正在于此。则此乃必无之理也。然则情无不善者。又何从得意之不善而明之乎。且必待意有不善而后。始加明之之功。则其所谓明之之功者。又何以异于诚之之功乎。盖多方推究而一未得其所安。则云峰之说。其亦终于差误而不可救解矣。
不善矣。则是已无不明矣。又安所容明之之功乎。苟可容明之之功。则又不足谓之无不善矣。若曰虽情无不善之人。而意念之随发者。则或不能无不善。故不可不加明之之功。则意无不善。而情有不善者或有之矣。未有情无不善而意有不善者也。若曰情之为理。本自无不善。不以贤愚而有异。必意而后始有善有不善。而贤愚之分。正在于此。则此乃必无之理也。然则情无不善者。又何从得意之不善而明之乎。且必待意有不善而后。始加明之之功。则其所谓明之之功者。又何以异于诚之之功乎。盖多方推究而一未得其所安。则云峰之说。其亦终于差误而不可救解矣。改本
情之发。不能纯一于善。须以意充扩而其意之发。又不能十分真实。一欲充扩其善端。(即章句所谓知为善而去恶。)一不欲充扩其善端(即章句所谓心之所发。有未实。)者。即所谓意有善有不善而不可不加诚之之功者也。禁止其不欲充扩善端之意。使欲充扩善端之意。十分真实。则意于是乎无不善。而即所谓诚之之功也。盖诚之之功。其所用力。只在于不欲充扩善端之意。若其欲充扩善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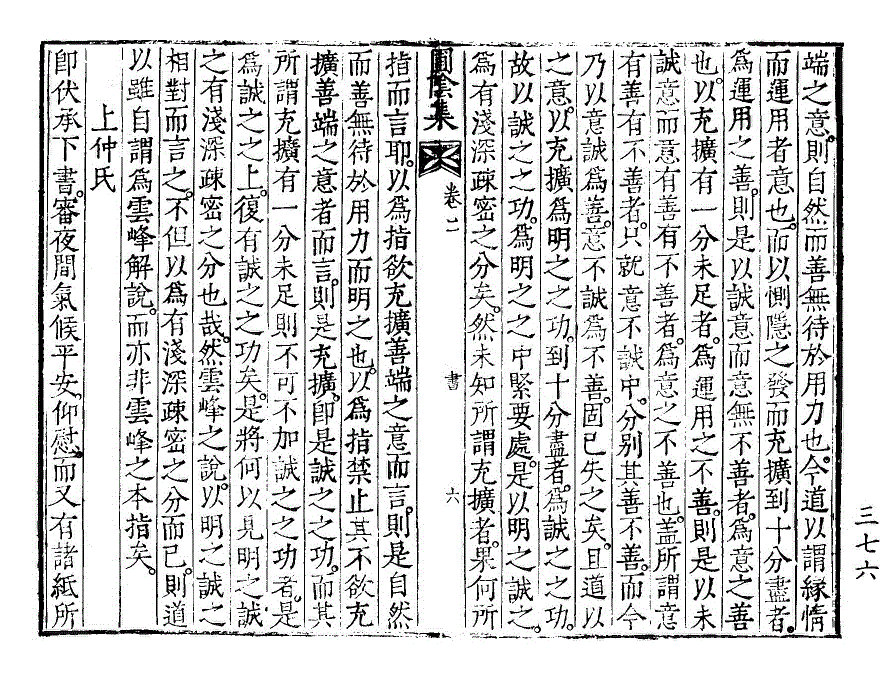 端之意。则自然而善无待于用力也。今道以谓缘情而运用者意也。而以恻隐之发而充扩到十分尽者。为运用之善。则是以诚意而意无不善者。为意之善也。以充扩有一分未足者。为运用之不善。则是以未诚意而意有善有不善者。为意之不善也。盖所谓意有善有不善者。只就意不诚中。分别其善不善。而今乃以意诚为善。意不诚为不善。固已失之矣。且道以之意。以充扩为明之之功。到十分尽者。为诚之之功。故以诚之之功。为明之之中紧要处。是以明之诚之。为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未知所谓充扩者。果何所指而言耶。以为指欲充扩善端之意而言。则是自然而善无待于用力而明之也。以为指禁止其不欲充扩善端之意者而言。则是充扩。即是诚之之功。而其所谓充扩有一分未足则不可不加诚之之功者。是为诚之之上。复有诚之之功矣。是将何以见明之诚之有浅深疏密之分也哉。然云峰之说。以明之诚之相对而言之。不但以为有浅深疏密之分而已。则道以虽自谓为云峰解说。而亦非云峰之本指矣。
端之意。则自然而善无待于用力也。今道以谓缘情而运用者意也。而以恻隐之发而充扩到十分尽者。为运用之善。则是以诚意而意无不善者。为意之善也。以充扩有一分未足者。为运用之不善。则是以未诚意而意有善有不善者。为意之不善也。盖所谓意有善有不善者。只就意不诚中。分别其善不善。而今乃以意诚为善。意不诚为不善。固已失之矣。且道以之意。以充扩为明之之功。到十分尽者。为诚之之功。故以诚之之功。为明之之中紧要处。是以明之诚之。为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未知所谓充扩者。果何所指而言耶。以为指欲充扩善端之意而言。则是自然而善无待于用力而明之也。以为指禁止其不欲充扩善端之意者而言。则是充扩。即是诚之之功。而其所谓充扩有一分未足则不可不加诚之之功者。是为诚之之上。复有诚之之功矣。是将何以见明之诚之有浅深疏密之分也哉。然云峰之说。以明之诚之相对而言之。不但以为有浅深疏密之分而已。则道以虽自谓为云峰解说。而亦非云峰之本指矣。上仲氏
即伏承下书。审夜间气候平安。仰慰。而又有诸纸所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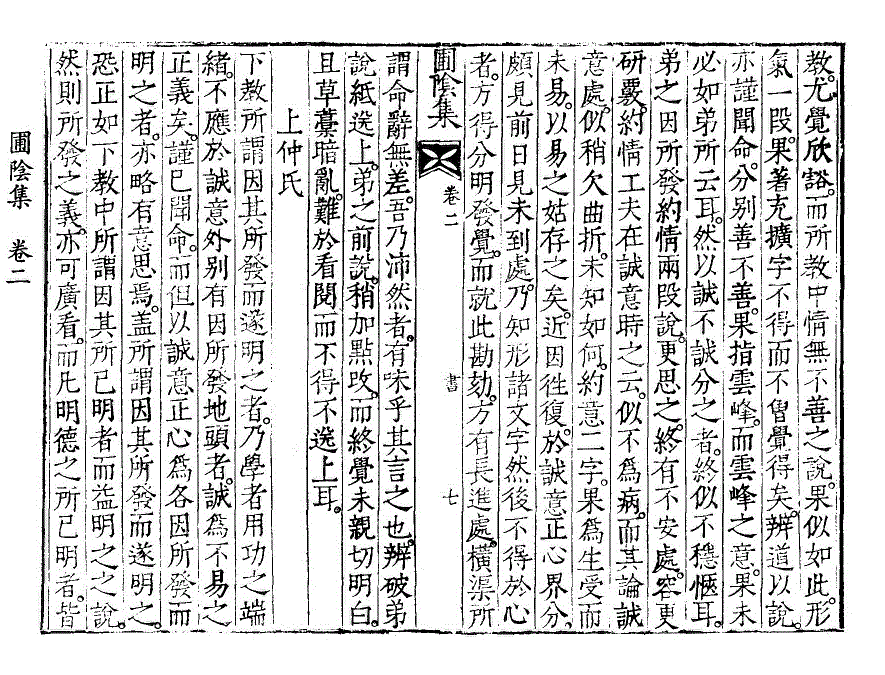 教。尤觉欣豁。而所教中情无不善之说。果似如此。形气一段。果著充扩字不得而不曾觉得矣。辨道以说。亦谨闻命。分别善不善。果指云峰。而云峰之意。果未必如弟所云耳。然以诚不诚分之者。终似不稳惬耳。弟之因所发约情两段说。更思之。终有不安处。容更研覈。约情工夫在诚意时之云。似不为病。而其论诚意处。似稍欠曲折。未知如何。约意二字。果为生受而未易。以易之姑存之矣。近因往复。于诚意正心界分。颇见前日见未到处。乃知形诸文字然后不得于心者。方得分明发觉。而就此勘劾。方有长进处。横渠所谓命辞无差。吾乃沛然者。有味乎其言之也。辨破弟说纸送上。弟之前说。稍加点改。而终觉未亲切明白。且草藁暗乱。难于看阅而不得不送上耳。
教。尤觉欣豁。而所教中情无不善之说。果似如此。形气一段。果著充扩字不得而不曾觉得矣。辨道以说。亦谨闻命。分别善不善。果指云峰。而云峰之意。果未必如弟所云耳。然以诚不诚分之者。终似不稳惬耳。弟之因所发约情两段说。更思之。终有不安处。容更研覈。约情工夫在诚意时之云。似不为病。而其论诚意处。似稍欠曲折。未知如何。约意二字。果为生受而未易。以易之姑存之矣。近因往复。于诚意正心界分。颇见前日见未到处。乃知形诸文字然后不得于心者。方得分明发觉。而就此勘劾。方有长进处。横渠所谓命辞无差。吾乃沛然者。有味乎其言之也。辨破弟说纸送上。弟之前说。稍加点改。而终觉未亲切明白。且草藁暗乱。难于看阅而不得不送上耳。上仲氏
下教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者。乃学者用功之端绪。不应于诚意外别有因所发地头者。诚为不易之正义矣。谨已闻命。而但以诚意正心为各因所发而明之者。亦略有意思焉。盖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恐正如下教中所谓因其所已明者而益明之之说。然则所发之义。亦可广看。而凡明德之所已明者。皆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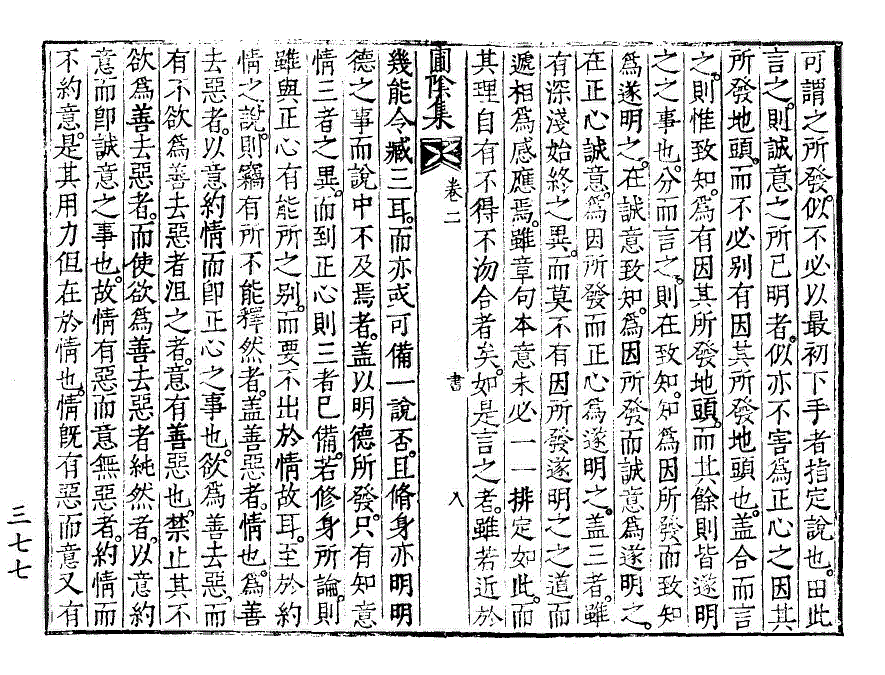 可谓之所发。似不必以最初下手者指定说也。田(一作由)此言之。则诚意之所已明者。似亦不害为正心之因其所发地头。而不必别有因其所发地头也。盖合而言之。则惟致知。为有因其所发地头。而其馀则皆遂明之之事也。分而言之。则在致知。知为因所发而致知为遂明之。在诚意致知。为因所发而诚意为遂明之。在正心诚意。为因所发而正心为遂明之。盖三者。虽有深浅始终之异。而莫不有因所发遂明之之道而递相为感应焉。虽章句本意未必一一排定如此。而其理自有不得不沕(一作吻)合者矣。如是言之者。虽若近于几能令臧三耳。而亦或可备一说否。且脩身亦明明德之事而说中不及焉者。盖以明德所发。只有知意情三者之异。而到正心则三者已备。若修身所论。则虽与正心有能所之别。而要不出于情故耳。至于约情之说。则窃有所不能释然者。盖善恶者。情也。为善去恶者。以意约情而即正心之事也。欲为善去恶。而有不欲为善去恶者沮之者。意有善恶也。禁止其不欲为善去恶者。而使欲为善去恶者纯然者。以意约意而即诚意之事也。故情有恶而意无恶者。约情而不约意。是其用力但在于情也。情既有恶而意又有
可谓之所发。似不必以最初下手者指定说也。田(一作由)此言之。则诚意之所已明者。似亦不害为正心之因其所发地头。而不必别有因其所发地头也。盖合而言之。则惟致知。为有因其所发地头。而其馀则皆遂明之之事也。分而言之。则在致知。知为因所发而致知为遂明之。在诚意致知。为因所发而诚意为遂明之。在正心诚意。为因所发而正心为遂明之。盖三者。虽有深浅始终之异。而莫不有因所发遂明之之道而递相为感应焉。虽章句本意未必一一排定如此。而其理自有不得不沕(一作吻)合者矣。如是言之者。虽若近于几能令臧三耳。而亦或可备一说否。且脩身亦明明德之事而说中不及焉者。盖以明德所发。只有知意情三者之异。而到正心则三者已备。若修身所论。则虽与正心有能所之别。而要不出于情故耳。至于约情之说。则窃有所不能释然者。盖善恶者。情也。为善去恶者。以意约情而即正心之事也。欲为善去恶。而有不欲为善去恶者沮之者。意有善恶也。禁止其不欲为善去恶者。而使欲为善去恶者纯然者。以意约意而即诚意之事也。故情有恶而意无恶者。约情而不约意。是其用力但在于情也。情既有恶而意又有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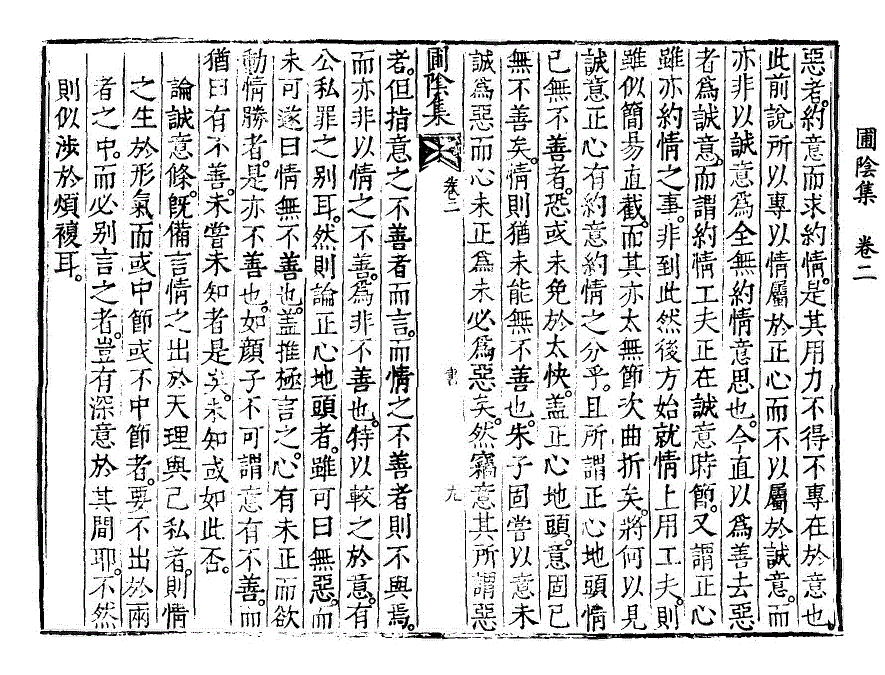 恶者。约意而求约情。是其用力不得不专在于意也。此前说所以专以情属于正心而不以属于诚意。而亦非以诚意为全无约情意思也。今直以为善去恶者为诚意。而谓约情工夫正在诚意时节。又谓正心虽亦约情之事。非到此然后方始就情上用工夫。则虽似简易直截。而其亦太无节次曲折矣。将何以见诚意正心有约意约情之分乎。且所谓正心地头情已无不善者。恐或未免于太快。盖正心地头。意固已无不善矣。情则犹未能无不善也。朱子固尝以意未诚为恶而心未正为未必为恶矣。然窃意其所谓恶者。但指意之不善者而言。而情之不善者则不与焉。而亦非以情之不善。为非不善也。特以较之于意。有公私罪之别耳。然则论正心地头者。虽可曰无恶。而未可遂曰情无不善也。盖推极言之。心有未正而欲动情胜者。是亦不善也。如颜子不可谓意有不善。而犹曰有不善。未尝未知者是矣。未知或如此否。
恶者。约意而求约情。是其用力不得不专在于意也。此前说所以专以情属于正心而不以属于诚意。而亦非以诚意为全无约情意思也。今直以为善去恶者为诚意。而谓约情工夫正在诚意时节。又谓正心虽亦约情之事。非到此然后方始就情上用工夫。则虽似简易直截。而其亦太无节次曲折矣。将何以见诚意正心有约意约情之分乎。且所谓正心地头情已无不善者。恐或未免于太快。盖正心地头。意固已无不善矣。情则犹未能无不善也。朱子固尝以意未诚为恶而心未正为未必为恶矣。然窃意其所谓恶者。但指意之不善者而言。而情之不善者则不与焉。而亦非以情之不善。为非不善也。特以较之于意。有公私罪之别耳。然则论正心地头者。虽可曰无恶。而未可遂曰情无不善也。盖推极言之。心有未正而欲动情胜者。是亦不善也。如颜子不可谓意有不善。而犹曰有不善。未尝未知者是矣。未知或如此否。论诚意条。既备言情之出于天理与己私者。则情之生于形气而或中节或不中节者。要不出于两者之中。而必别言之者。岂有深意于其间耶。不然则似涉于烦复耳。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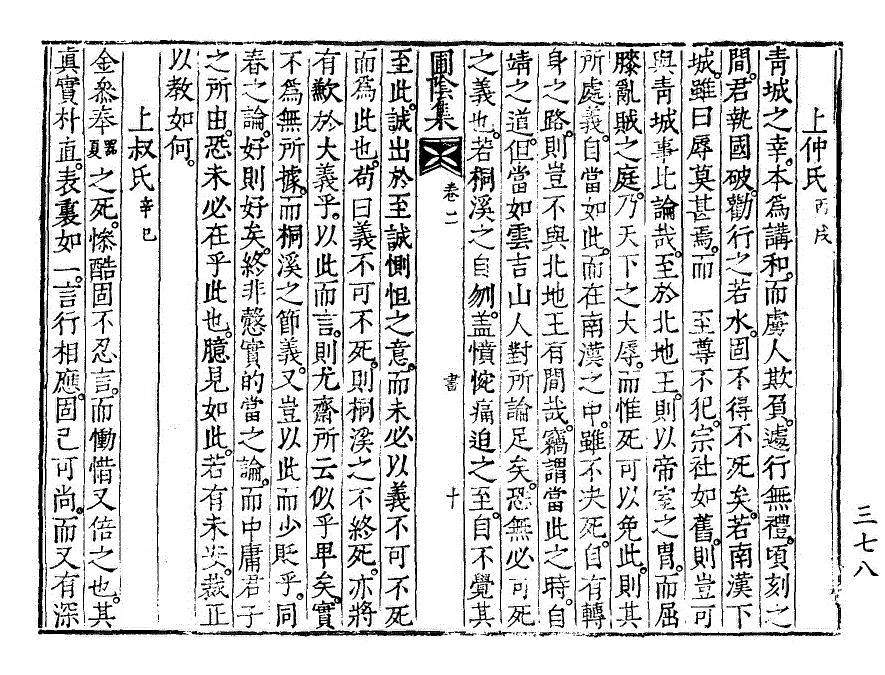 上仲氏(丙戌)
上仲氏(丙戌)青城之幸。本为讲和。而虏人欺负。遽行无礼。顷刻之间。君执国破。劝行之若水。固不得不死矣。若南汉下城。虽曰辱莫甚焉。而 至尊不犯。宗社如旧。则岂可与青城事比论哉。至于北地王。则以帝室之胄。而屈膝乱贼之庭。乃天下之大辱。而惟死可以免此。则其所处义。自当如此。而在南汉之中。虽不决死。自有转身之路。则岂不与北地王有间哉。窃谓当此之时。自靖之道。但当如云吉山人对所论足矣。恐无必可死之义也。若桐溪之自刎。盖愤惋痛迫之至。自不觉其至此。诚出于至诚恻怛之意。而未必以义不可不死而为此也。苟曰义不可不死。则桐溪之不终死。亦将有歉于大义乎。以此而言。则尤斋所云似乎卑矣。实不为无所据。而桐溪之节义。又岂以此而少贬乎。同春之论。好则好矣。终非悫实的当之论。而中庸君子之所由。恐未必在乎此也。臆见如此。若有未安。裁正以教如何。
上叔氏(辛巳)
金参奉(器夏)之死。惨酷固不忍言。而恸惜又倍之也。其真实朴直。表里如一。言行相应。固已可尚。而又有深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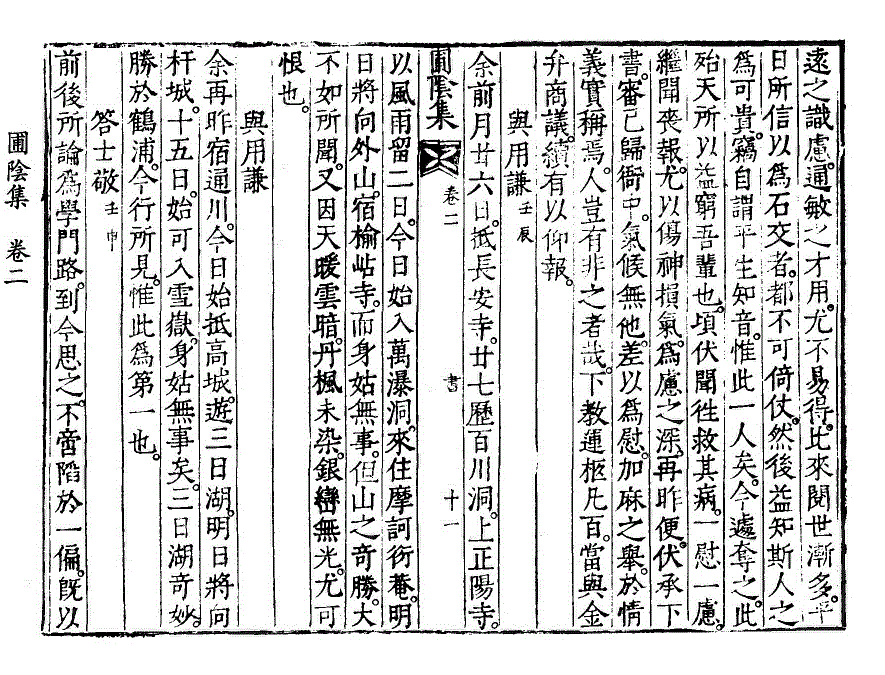 远之识虑。通敏之才用。尤不易得。比来阅世渐多。平日所信以为石交者。都不可倚仗。然后益知斯人之为可贵。窃自谓平生知音。惟此一人矣。今遽夺之。此殆天所以益穷吾辈也。顷伏闻往救其病。一慰一虑。继闻丧报。尤以伤神损气。为虑之深。再昨便。伏承下书。审已归衙中。气候无他。差以为慰。加麻之举。于情义实称焉。人岂有非之者哉。下教运柩凡百。当与金弁商议。续有以仰报。
远之识虑。通敏之才用。尤不易得。比来阅世渐多。平日所信以为石交者。都不可倚仗。然后益知斯人之为可贵。窃自谓平生知音。惟此一人矣。今遽夺之。此殆天所以益穷吾辈也。顷伏闻往救其病。一慰一虑。继闻丧报。尤以伤神损气。为虑之深。再昨便。伏承下书。审已归衙中。气候无他。差以为慰。加麻之举。于情义实称焉。人岂有非之者哉。下教运柩凡百。当与金弁商议。续有以仰报。与用谦(壬辰)
余前月廿六日。抵长安寺。廿七历百川洞。上正阳寺。以风雨留二日。今日始入万瀑洞。来住摩诃衍庵。明日将向外山。宿榆岾寺。而身姑无事。但山之奇胜。大不如所闻。又因天暖云暗。丹枫未染。银峦无光。尤可恨也。
与用谦
余再昨宿通川。今日始抵高城。游三日湖。明日将向杆城。十五日。始可入雪岳。身姑无事矣。三日湖奇妙。胜于鹤浦。今行所见。惟此为第一也。
答士敬(壬申)
前后所论为学门路。到今思之。不啻陷于一偏。既以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79L 页
 自误。复以误人。一至于此。此实妄率浮躁。轻为大言所致。念之惶惧。无地自容。窃谓为学门路。有博约两端而决不容偏废。上自孔孟。下至程朱。其设教莫不如此。此实亘古亘今之常法而不可有违者也。间或有偏主约礼之说者。此不过一时矫弊之权宜而非可通行者也。今乃不遵亘古亘今之常法。而反以一时权宜之说蔽之者。岂不大误哉。愿士敬。自今以往。扫去旧闻。更立新规。其应接事物时。力加持守。略依前日所讲。存心节度。而但得无事时。即便着实读书。不遗馀力。若终日无事。便可终日读书。不必别为静坐之计。若读书。惟事泛博。则固妨于存心。若务要精熟。则不惟不妨于存心。反为存心之妙法。不必兀然静坐然后可以存心也。且读书精熟。则不惟可以穷理。存心自在其中。兀然静坐。则不但欠却穷理工夫。其所谓存心者。亦昏昧儱侗而无进步处。一则两得。一则两失。此不可不知也。士敬曾言诵夙兴夜寐箴时觉意味自好。此亦存养佳法。而缉乃驳之以为不可。只依靠此等而不于静坐时用工者。极有弊病。惟士敬察之。
自误。复以误人。一至于此。此实妄率浮躁。轻为大言所致。念之惶惧。无地自容。窃谓为学门路。有博约两端而决不容偏废。上自孔孟。下至程朱。其设教莫不如此。此实亘古亘今之常法而不可有违者也。间或有偏主约礼之说者。此不过一时矫弊之权宜而非可通行者也。今乃不遵亘古亘今之常法。而反以一时权宜之说蔽之者。岂不大误哉。愿士敬。自今以往。扫去旧闻。更立新规。其应接事物时。力加持守。略依前日所讲。存心节度。而但得无事时。即便着实读书。不遗馀力。若终日无事。便可终日读书。不必别为静坐之计。若读书。惟事泛博。则固妨于存心。若务要精熟。则不惟不妨于存心。反为存心之妙法。不必兀然静坐然后可以存心也。且读书精熟。则不惟可以穷理。存心自在其中。兀然静坐。则不但欠却穷理工夫。其所谓存心者。亦昏昧儱侗而无进步处。一则两得。一则两失。此不可不知也。士敬曾言诵夙兴夜寐箴时觉意味自好。此亦存养佳法。而缉乃驳之以为不可。只依靠此等而不于静坐时用工者。极有弊病。惟士敬察之。即今所读何书。曾欲看朱书节要。今果看之否。因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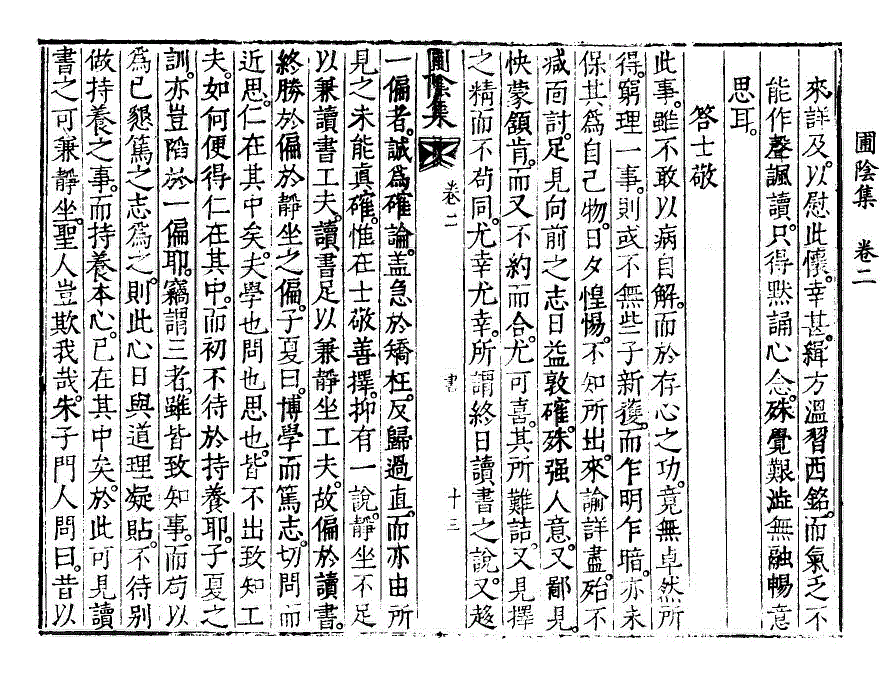 来详及。以慰此怀。幸甚。缉方温习西铭。而气乏不能作声讽读。只得默诵心念。殊觉艰涩无融畅意思耳。
来详及。以慰此怀。幸甚。缉方温习西铭。而气乏不能作声讽读。只得默诵心念。殊觉艰涩无融畅意思耳。答士敬
此事。虽不敢以病自解。而于存心之功。竟无卓然所得。穷理一事。则或不无些子新获。而乍明乍暗。亦未保其为自己物。日夕惶惕。不知所出。来谕详尽。殆不减面讨。足见向前之志日益敦确。殊强人意。又鄙见。快蒙颔肯。而又不约而合。尤可喜。其所难诘。又见择之精而不苟同。尤幸尤幸。所谓终日读书之说。又趍一偏者。诚为确论。盖急于矫枉。反归过直。而亦由所见之未能真确。惟在士敬善择。抑有一说。静坐不足以兼读书工夫。读书足以兼静坐工夫。故偏于读书。终胜于偏于静坐之偏。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夫学也问也思也。皆不出致知工夫。如何便得仁在其中。而初不待于持养耶。子夏之训。亦岂陷于一偏耶。窃谓三者。虽皆致知事。而苟以为已恳笃之志为之。则此心日与道理凝贴。不待别做持养之事。而持养本心。已在其中矣。于此可见读书之可兼静坐。圣人岂欺我哉。朱子门人问曰。昔以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0L 页
 观书为致知之方。今又见得是养心之法。朱子曰。较宽不急迫。又曰。一举两得。一边又存得心。一边理又到此。亦与子夏之训。若合符节。凡此类非止一二。不胜枚举。况为学之道。虽有不易之大法。又当随学者之资禀而抑扬之。如士敬资禀。自是长于持守而短于见解。尤当以读书为重。虽以大学次序论之。格致居先而诚正居后。在初学。固当以读书为先。是则又非有变于不易之大法者矣。况士敬年纪将近不惑。天下义理。尽无穷尽。今虽汲汲读书。未见其有馀。朱子所谓中年以后尤当汲汲者。不可不深念而勇遵也。然终日读书不遗馀力之说。终欠从容不迫意思。此则终不可据为定论也。所经营大事。才因万顷兄主。略闻曲折。此固人子所不容已处。苟能无以固必之私害其心术之正。则无往而非用力处。岂但以读书为学哉。
观书为致知之方。今又见得是养心之法。朱子曰。较宽不急迫。又曰。一举两得。一边又存得心。一边理又到此。亦与子夏之训。若合符节。凡此类非止一二。不胜枚举。况为学之道。虽有不易之大法。又当随学者之资禀而抑扬之。如士敬资禀。自是长于持守而短于见解。尤当以读书为重。虽以大学次序论之。格致居先而诚正居后。在初学。固当以读书为先。是则又非有变于不易之大法者矣。况士敬年纪将近不惑。天下义理。尽无穷尽。今虽汲汲读书。未见其有馀。朱子所谓中年以后尤当汲汲者。不可不深念而勇遵也。然终日读书不遗馀力之说。终欠从容不迫意思。此则终不可据为定论也。所经营大事。才因万顷兄主。略闻曲折。此固人子所不容已处。苟能无以固必之私害其心术之正。则无往而非用力处。岂但以读书为学哉。答士敬
缉五月复书中所陈。追而思之。终是偏颇不平正。士敬前日之疑为得之。今云诚然。书绅反误入矣。盖古之圣贤所以教告后学。以入德之门。至评至明。至平至正。今但当谨守其说而笃行之。又何必自立新说。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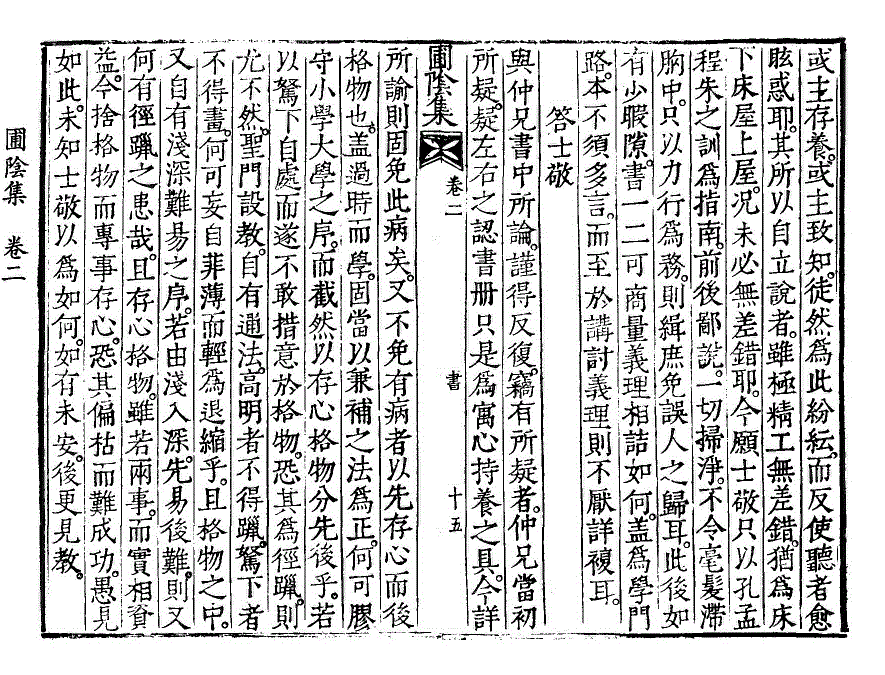 或主存养。或主致知。徒然为此纷纭。而反使听者愈眩惑耶。其所以自立说者。虽极精工无差错。犹为床下床屋上屋。况未必无差错耶。今愿士敬只以孔孟程朱之训为指南。前后鄙说。一切扫净。不令毫发滞胸中。只以力行为务。则缉庶免误人之归耳。此后如有少暇隙。书一二可商量义理相诘如何。盖为学门路。本不须多言。而至于讲讨义理则不厌详复耳。
或主存养。或主致知。徒然为此纷纭。而反使听者愈眩惑耶。其所以自立说者。虽极精工无差错。犹为床下床屋上屋。况未必无差错耶。今愿士敬只以孔孟程朱之训为指南。前后鄙说。一切扫净。不令毫发滞胸中。只以力行为务。则缉庶免误人之归耳。此后如有少暇隙。书一二可商量义理相诘如何。盖为学门路。本不须多言。而至于讲讨义理则不厌详复耳。答士敬
与仲兄书中所论。谨得反复。窃有所疑者。仲兄当初所疑。疑左右之认书册只是为寓心持养之具。今详所谕则固免此病矣。又不免有病者以先存心而后格物也。盖过时而学。固当以兼补之法为正。何可胶守小学大学之序。而截然以存心格物分先后乎。若以驽下自处而遂不敢措意于格物。恐其为径躐。则尤不然。圣门设教。自有通法。高明者不得躐。驽下者不得画。何可妄自菲薄而轻为退缩乎。且格物之中。又自有浅深难易之序。若由浅入深。先易后难。则又何有径躐之患哉。且存心格物。虽若两事。而实相资益。今舍格物而专事存心。恐其偏枯而难成功。愚见如此。未知士敬以为如何。如有未安。后更见教。
答士敬(癸酉)
西铭。略略收拾。而终未能专一下工。尚何可与议于精熟无疑乎。闻方温大学。甚善。此亦欲稍待西铭温过。即理此书。近来觉得此书甚是要本。苟理会得透彻。一生用之不尽矣。忘忽之戒。敦厚之赠。警于昏愦者深矣。敢不书绅从事。但好笑二字。未安。朋友之间。苟见所失。当正色严辞。俾有以警动。又何必杂以戏笑。以相假饶耶。此后如有所欲言。固当肆意竭论。使不陷于坑堑。是乃朋友相救之道。切不可为此等态度也。如何如何。
答金进士(楷○癸未)
下询深衣制度。谨考琼山,久庵之说写誊。兼附鄙见以上。伏乞有以裁定。幸甚。鄙说质之家仲兄。亦无异意矣。
别纸
深衣制度。全无讲明之素矣。今下询之勤。不远千里。不可诿以不知而阙然无报。以孤好问之盛意。故猝取家礼及诸家之说而考究之。则亦不无可言者矣。盖家礼。既不详著领制。其所谓两襟交掩两领之会自方者。诚莫晓其所以然。其见于图者。则犹可谓方。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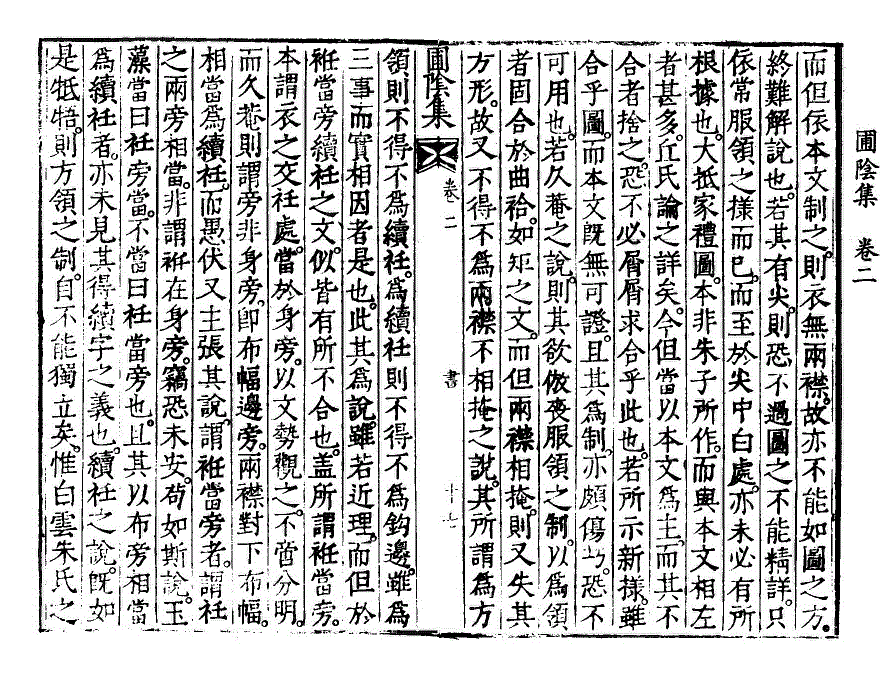 而但依本文制之。则衣无两襟。故亦不能如图之方。终难解说也。若其有尖。则恐不过图之不能精详。只依常服领之㨾而已。而至于尖中白处。亦未必有所根据也。大抵家礼图。本非朱子所作。而与本文相左者甚多。丘氏论之详矣。今但当以本文为主。而其不合者舍之。恐不必屑屑求合乎此也。若所示新㨾。虽合乎图。而本文既无可證。且其为制。亦颇伤巧。恐不可用也。若久庵之说。则其欲仿丧服领之制。以为领者固合于曲袷。如矩之文。而但两襟相掩。则又失其方形。故又不得不为两襟不相掩之说。其所谓为方领则不得不为续衽。为续衽则不得不为钩边。虽为三事而实相因者是也。此其为说。虽若近理。而但于衽当旁续衽之文。似皆有所不合也。盖所谓衽当旁。本谓衣之交衽处。当于身旁。以文势观之。不啻分明。而久庵则谓旁非身旁。即布幅边旁。两襟对下布幅。相当为续衽。而愚伏又主张其说。谓衽当旁者。谓衽之两旁相当。非谓衽在身旁。窃恐未安。苟如斯说。玉藻当曰衽旁当。不当曰衽当旁也。且其以布旁相当为续衽者。亦未见其得续字之义也。续衽之说。既如是牴牾。则方领之制。自不能独立矣。惟白云朱氏之
而但依本文制之。则衣无两襟。故亦不能如图之方。终难解说也。若其有尖。则恐不过图之不能精详。只依常服领之㨾而已。而至于尖中白处。亦未必有所根据也。大抵家礼图。本非朱子所作。而与本文相左者甚多。丘氏论之详矣。今但当以本文为主。而其不合者舍之。恐不必屑屑求合乎此也。若所示新㨾。虽合乎图。而本文既无可證。且其为制。亦颇伤巧。恐不可用也。若久庵之说。则其欲仿丧服领之制。以为领者固合于曲袷。如矩之文。而但两襟相掩。则又失其方形。故又不得不为两襟不相掩之说。其所谓为方领则不得不为续衽。为续衽则不得不为钩边。虽为三事而实相因者是也。此其为说。虽若近理。而但于衽当旁续衽之文。似皆有所不合也。盖所谓衽当旁。本谓衣之交衽处。当于身旁。以文势观之。不啻分明。而久庵则谓旁非身旁。即布幅边旁。两襟对下布幅。相当为续衽。而愚伏又主张其说。谓衽当旁者。谓衽之两旁相当。非谓衽在身旁。窃恐未安。苟如斯说。玉藻当曰衽旁当。不当曰衽当旁也。且其以布旁相当为续衽者。亦未见其得续字之义也。续衽之说。既如是牴牾。则方领之制。自不能独立矣。惟白云朱氏之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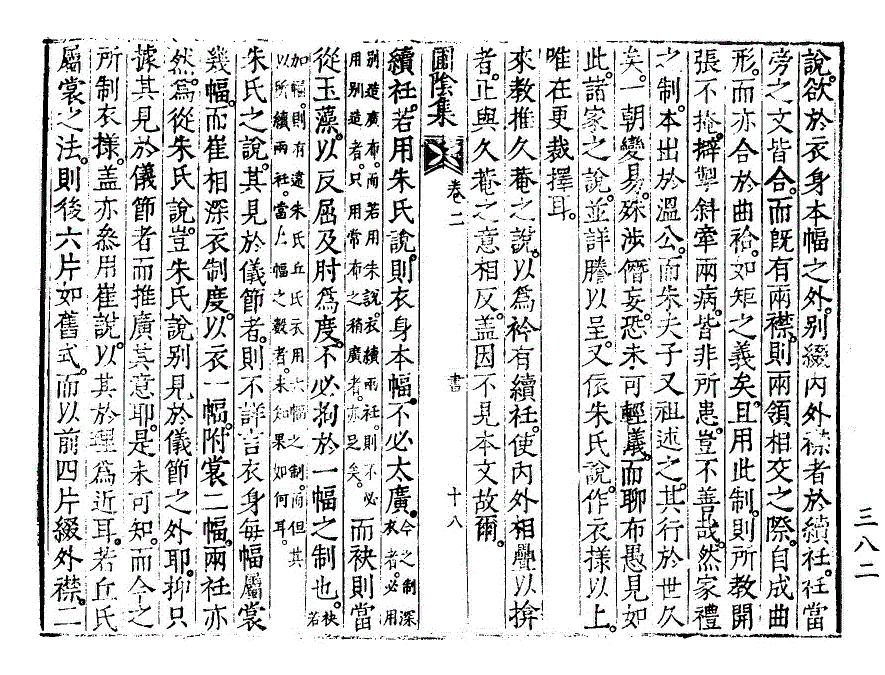 说。欲于衣身本幅之外。别缀内外襟者于续衽。衽当旁之文皆合。而既有两襟。则两领相交之际。自成曲形。而亦合于曲袷。如矩之义矣。且用此制。则所教开张不掩。擗掣斜牵两病。皆非所患。岂不善哉。然家礼之制。本出于温公。而朱夫子又祖述之。其行于世久矣。一朝变易。殊涉僭妄。恐未可轻议。而聊布愚见如此。诸家之说。并详誊以呈。又依朱氏说。作衣㨾以上。唯在更裁择耳。
说。欲于衣身本幅之外。别缀内外襟者于续衽。衽当旁之文皆合。而既有两襟。则两领相交之际。自成曲形。而亦合于曲袷。如矩之义矣。且用此制。则所教开张不掩。擗掣斜牵两病。皆非所患。岂不善哉。然家礼之制。本出于温公。而朱夫子又祖述之。其行于世久矣。一朝变易。殊涉僭妄。恐未可轻议。而聊布愚见如此。诸家之说。并详誊以呈。又依朱氏说。作衣㨾以上。唯在更裁择耳。来教推久庵之说。以为衿有续衽。使内外相叠以掩者。正与久庵之意相反。盖因不见本文故尔。
续衽。若用朱氏说。则衣身本幅。不必太广。(今之制深衣者。必用别造广布。而若用朱说。衣续两衽。则不必用别造者。只用常布之稍广者。亦足矣。)而袂则当从玉藻。以反屈及肘为度。不必拘于一幅之制也。(袂若加幅。则有违朱氏丘氏衣用六幅之制。而但其以所续两衽。当二幅之数者。未知果如何耳。)
朱氏之说。其见于仪节者。则不详言衣身每幅属裳几幅。而崔相深衣制度。以衣一幅。附裳二幅。两衽亦然。为从朱氏说。岂朱氏说别见于仪节之外耶。抑只据其见于仪节者而推广其意耶。是未可知。而今之所制衣㨾。盖亦参用崔说。以其于理为近耳。若丘氏属裳之法。则后六片如旧式。而以前四片缀外襟。二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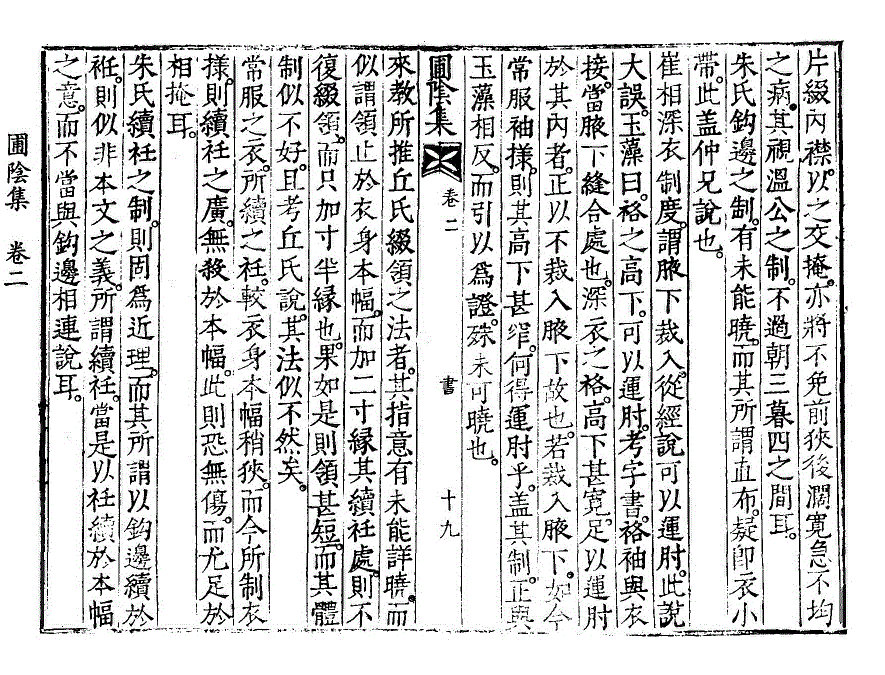 片缀内襟。以之交掩。亦将不免前狭后阔宽急不均之病。其视温公之制。不过朝三暮四之间耳。
片缀内襟。以之交掩。亦将不免前狭后阔宽急不均之病。其视温公之制。不过朝三暮四之间耳。朱氏钩边之制。有未能晓。而其所谓直布。疑即衣小带。此盖仲兄说也。
崔相深衣制度。谓腋下裁入。从经说可以运肘。此说大误。玉藻曰。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考字书。袼袖与衣接。当腋下缝合处也。深衣之袼。高下甚宽。足以运肘于其内者。正以不裁入腋下故也。若裁入腋下。如今常服袖㨾。则其高下甚窄。何得运肘乎。盖其制。正与玉藻相反。而引以为證。殊未可晓也。
来教所推丘氏缀领之法者。其指意有未能详晓。而似谓领止于衣身本幅。而加二寸缘其续衽处。则不复缀领。而只加寸半缘也。果如是则领甚短。而其体制似不好。且考丘氏说。其法似不然矣。
常服之衣。所续之衽。较衣身本幅稍狭。而今所制衣㨾。则续衽之广。无杀于本幅。此则恐无伤。而尤足于相掩耳。
朱氏续衽之制。则固为近理。而其所谓以钩边续于衽。则似非本文之义。所谓续衽。当是以衽续于本幅之意。而不当与钩边相连说耳。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3L 页
 丘氏欲以玉藻制十有二幅之文。通衣裳看。于文势则诚然。未知果如何也。
丘氏欲以玉藻制十有二幅之文。通衣裳看。于文势则诚然。未知果如何也。答金进士(楷)
下示深衣说。用意精深。命辞明切。虽少年精力。岂易及此。深可钦叹。而但往往稍有牵强之处。恐缘必欲傅会朱子而然耳。区区所见既如此。而勤问之意。又不可孤。辄敢逐条论列如左。僭妄之罪。无所逃矣。然其为说。未必中理。制造之际。不足以此而有所拘碍也。所辨诸家之谬。皆为切当。而其中所论裳制。亦似得之矣。
领
领之新㨾。端整紧密。便于服着。亦可谓善矣。而證之于古。古注疏所云如小儿衣领及拥咽者。虽未详其制。而窃疑其与此相近。则又不为无所据者矣。然若谓朱子旧制亦是如此。则恐未然也。夫家礼所谓两襟交掩而衽在腋下。则两领之会自方者。详其文意。盖曰必两襟交掩而衽当腋下。然后左右斜互之极。而两领相接之际。始成方形云尔。则其领之本不方裁。自可见矣。苟其方裁。则不待襟之交掩而领固已方矣。又何必云云哉。且蔡氏所述朱子说方领。只是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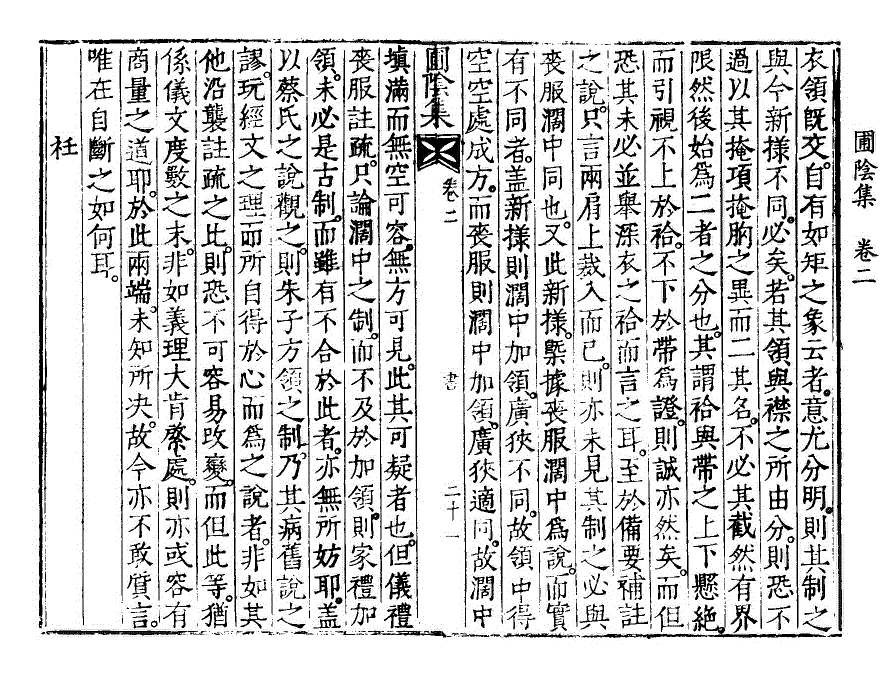 衣领既交。自有如矩之象云者。意尤分明。则其制之与今新㨾不同。必矣。若其领与襟之所由分。则恐不过以其掩项掩胸之异而二其名。不必其截然有界限然后始为二者之分也。其谓袷与带之上下悬绝。而引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为證。则诚亦然矣。而但恐其未必并举深衣之袷而言之耳。至于备要补注之说。只言两肩上裁入而已。则亦未见其制之必与丧服阔中同也。又此新㨾。槩据丧服阔中为说。而实有不同者。盖新㨾则阔中加领。广狭不同。故领中得空空处成方。而丧服则阔中加领。广狭适同。故阔中填满而无空可容。无方可见。此其可疑者也。但仪礼丧服注疏。只论阔中之制。而不及于加领。则家礼加领。未必是古制。而虽有不合于此者。亦无所妨耶。盖以蔡氏之说观之。则朱子方领之制。乃其病旧说之谬。玩经文之理而所自得于心而为之说者。非如其他沿袭注疏之比。则恐不可容易改变。而但此等。犹系仪文度数之末。非如义理大肯綮处。则亦或容有商量之道耶。于此两端。未知所决。故今亦不敢质言。唯在自断之如何耳。
衣领既交。自有如矩之象云者。意尤分明。则其制之与今新㨾不同。必矣。若其领与襟之所由分。则恐不过以其掩项掩胸之异而二其名。不必其截然有界限然后始为二者之分也。其谓袷与带之上下悬绝。而引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为證。则诚亦然矣。而但恐其未必并举深衣之袷而言之耳。至于备要补注之说。只言两肩上裁入而已。则亦未见其制之必与丧服阔中同也。又此新㨾。槩据丧服阔中为说。而实有不同者。盖新㨾则阔中加领。广狭不同。故领中得空空处成方。而丧服则阔中加领。广狭适同。故阔中填满而无空可容。无方可见。此其可疑者也。但仪礼丧服注疏。只论阔中之制。而不及于加领。则家礼加领。未必是古制。而虽有不合于此者。亦无所妨耶。盖以蔡氏之说观之。则朱子方领之制。乃其病旧说之谬。玩经文之理而所自得于心而为之说者。非如其他沿袭注疏之比。则恐不可容易改变。而但此等。犹系仪文度数之末。非如义理大肯綮处。则亦或容有商量之道耶。于此两端。未知所决。故今亦不敢质言。唯在自断之如何耳。衽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4L 页
 所谓朱子改作之说。有何所据耶。今以杨氏说观之。则但言先生晚岁所服深衣。去旧说曲裾之制而不用而已。未见其有改作意思耳。
所谓朱子改作之说。有何所据耶。今以杨氏说观之。则但言先生晚岁所服深衣。去旧说曲裾之制而不用而已。未见其有改作意思耳。所谓上下衽相续者。未知续衽之义果如此否耳。
愚于续衽之说。犹有所疑者。盖以孔子被发左衽之言观之。古人衣服之必左右交掩可见。而衰服亦是无衽之衣。则以之交掩。亦将不免前后宽急不均之病。一如深衣矣。衰服。乃是古制。则岂古人衣服本来如此耶。然则何独于深衣。疑其无衽而必欲续之耶。今欲理会深衣之制。恐须先理会衰服。乃为有本源。而可免于杜撰之诮耳。
袂
所谓以二幅各属于左右者。今详家礼文义。恐未然。苟其然者。当曰用布四幅。何得但云二幅哉。盖既曰用布。则须举其容入之全数而言。不应偏指一袖所用耳。且今人所造深衣。多用一幅布为袖。而不至如半臂之短。但未能反屈及肘而已。今此所论。似乎过矣。(观上文。于衣曰用布二幅。于裳曰用布六幅者。则尤可晓然矣。)
缘
用寸半似当。而里面不缘。亦可矣。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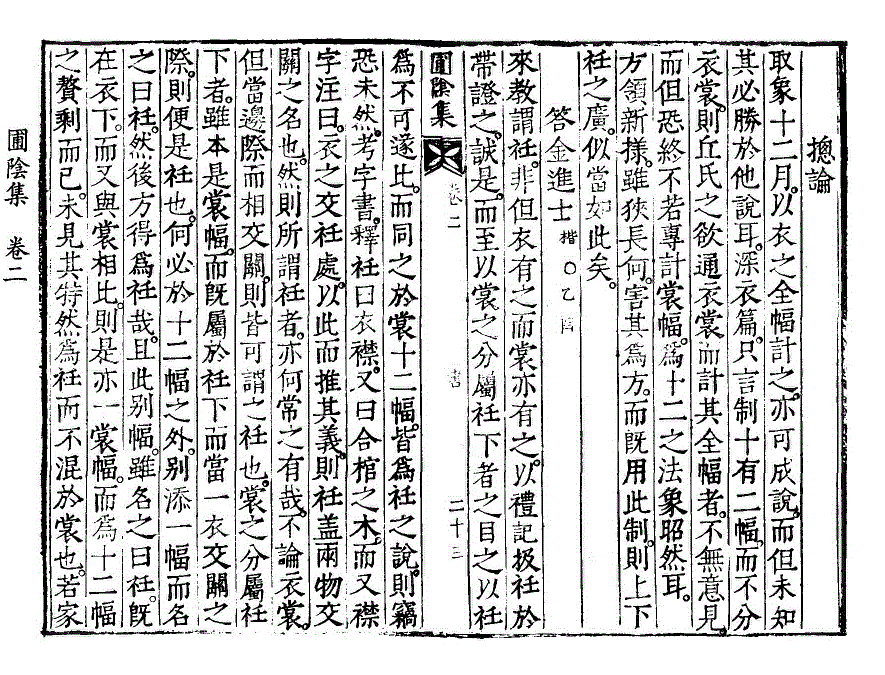 总论
总论取象十二月。以衣之全幅计之。亦可成说。而但未知其必胜于他说耳。深衣篇。只言制十有二幅。而不分衣裳。则丘氏之欲通衣裳而计其全幅者。不无意见。而但恐终不若专计裳幅。为十二之法象昭然耳。
方领新㨾。虽狭长何。害其为方。而既用此制。则上下衽之广。似当如此矣。
答金进士(楷○乙酉)
来教谓衽。非但衣有之而裳亦有之。以礼记扱衽于带證之。诚是。而至以裳之分属衽下者之目之以衽为不可遂比。而同之于裳十二幅。皆为衽之说。则窃恐未然。考字书。释衽曰衣襟。又曰合棺之木。而又襟字注曰。衣之交衽处。以此而推其义。则衽盖两物交关之名也。然则所谓衽者。亦何常之有哉。不论衣裳。但当边际而相交关。则皆可谓之衽也。裳之分属衽下者。虽本是裳幅。而既属于衽下而当一衣交关之际。则便是衽也。何必于十二幅之外。别添一幅而名之曰衽。然后方得为衽哉。且此别幅。虽名之曰衽。既在衣下。而又与裳相比。则是亦一裳幅。而为十二幅之赘剩而已。未见其特然为衽而不混于裳也。若家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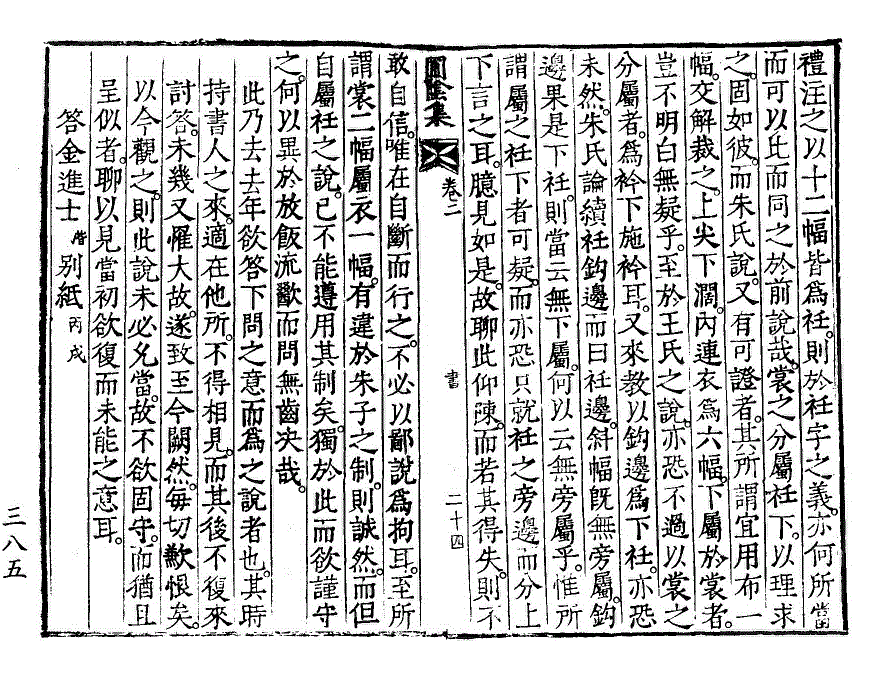 礼注之以十二幅皆为衽。则于衽字之义。亦何所当而可以比而同之于前说哉。裳之分属衽下。以理求之。固如彼。而朱氏说。又有可證者。其所谓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阔。内连衣为六幅。下属于裳者。岂不明白无疑乎。至于王氏之说。亦恐不过以裳之分属者。为衿下施衿耳。又来教以钩边为下衽。亦恐未然。朱氏论续衽钩边而曰衽边。斜幅既无旁属。钩边果是下衽。则当云无下属。何以云无旁属乎。惟所谓属之衽下者可疑。而亦恐只就衽之旁边而分上下言之耳。臆见如是。故聊此仰陈。而若其得失。则不敢自信。唯在自断而行之。不必以鄙说为拘耳。至所谓裳二幅属衣一幅。有违于朱子之制。则诚然。而但自属衽之说。已不能遵用其制矣。独于此而欲谨守之。何以异于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哉。
礼注之以十二幅皆为衽。则于衽字之义。亦何所当而可以比而同之于前说哉。裳之分属衽下。以理求之。固如彼。而朱氏说。又有可證者。其所谓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阔。内连衣为六幅。下属于裳者。岂不明白无疑乎。至于王氏之说。亦恐不过以裳之分属者。为衿下施衿耳。又来教以钩边为下衽。亦恐未然。朱氏论续衽钩边而曰衽边。斜幅既无旁属。钩边果是下衽。则当云无下属。何以云无旁属乎。惟所谓属之衽下者可疑。而亦恐只就衽之旁边而分上下言之耳。臆见如是。故聊此仰陈。而若其得失。则不敢自信。唯在自断而行之。不必以鄙说为拘耳。至所谓裳二幅属衣一幅。有违于朱子之制。则诚然。而但自属衽之说。已不能遵用其制矣。独于此而欲谨守之。何以异于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哉。此乃去去年欲答下问之意而为之说者也。其时持书人之来。适在他所。不得相见。而其后不复来讨答。未几又罹大故。遂致至今阙然。每切歉恨矣。以今观之。则此说未必允当。故不欲固守。而犹且呈似者。聊以见当初欲复而未能之意耳。
答金进士(楷)别纸(丙戌)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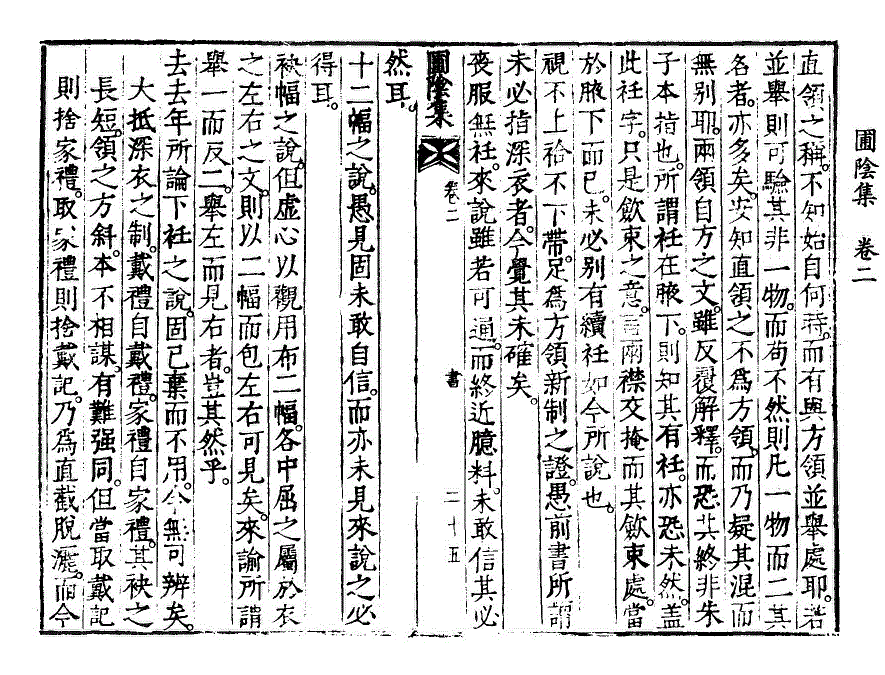 直领之称。不知始自何时。而有与方领并举处耶。若并举则可验其非一物。而苟不然则凡一物而二其名者。亦多矣。安知直领之不为方领。而乃疑其混而无别耶。两领自方之文。虽反覆解释。而恐其终非朱子本指也。所谓衽在腋下。则知其有衽。亦恐未然。盖此衽字。只是敛束之意。言两襟交掩而其敛束处。当于腋下而已。未必别有续衽如今所说也。
直领之称。不知始自何时。而有与方领并举处耶。若并举则可验其非一物。而苟不然则凡一物而二其名者。亦多矣。安知直领之不为方领。而乃疑其混而无别耶。两领自方之文。虽反覆解释。而恐其终非朱子本指也。所谓衽在腋下。则知其有衽。亦恐未然。盖此衽字。只是敛束之意。言两襟交掩而其敛束处。当于腋下而已。未必别有续衽如今所说也。视不上袷不下带。足为方领新制之證。愚前书所谓未必指深衣者。今觉其未确矣。
丧服无衽。来说虽若可通。而终近臆料。未敢信其必然耳。
十二幅之说。愚见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见来说之必得耳。
袂幅之说。但虚心以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属于衣之左右之文。则以二幅而包左右可见矣。来谕所谓举一而反二。举左而见右者。岂其然乎。
去去年所论下衽之说。固已弃而不用。今无可辨矣。
大抵深衣之制。戴礼自戴礼。家礼自家礼。其袂之长短。领之方斜。本不相谋。有难强同。但当取戴记则舍家礼。取家礼则舍戴记。乃为直截脱洒。而今
圃阴集卷之二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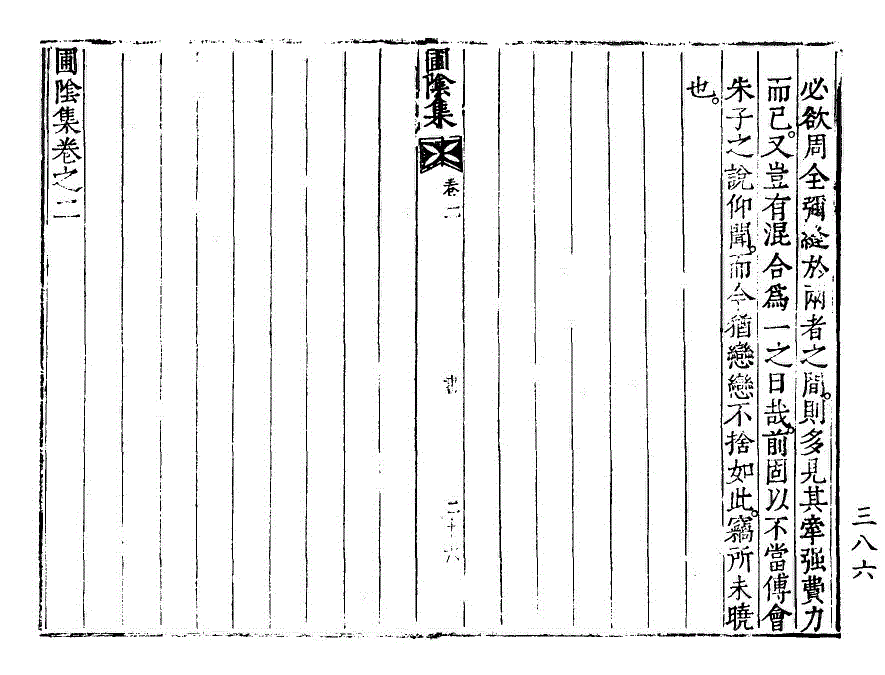 必欲周全弥缝于两者之间。则多见其牵强费力而已。又岂有混合为一之日哉。前固以不当傅会朱子之说仰闻。而今犹恋恋不舍如此。窃所未晓也。
必欲周全弥缝于两者之间。则多见其牵强费力而已。又岂有混合为一之日哉。前固以不当傅会朱子之说仰闻。而今犹恋恋不舍如此。窃所未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