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书
书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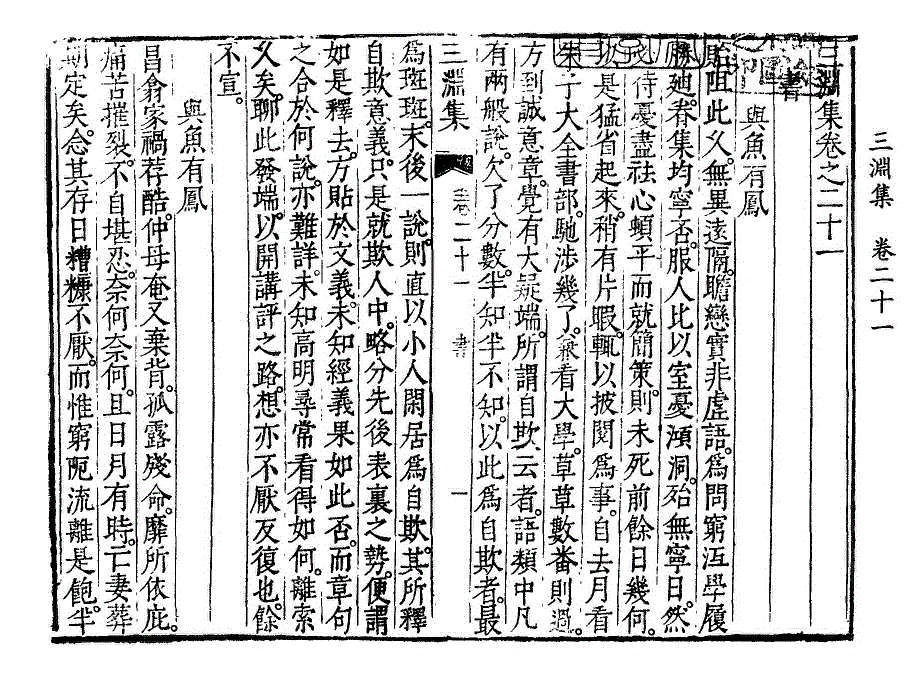 与鱼有凤
与鱼有凤贻阻此久。无异远隔。瞻恋实非虚语。为问穷冱学履胜迪。眷集均宁否。服人比以室忧澒洞。殆无宁日。然必待忧尽祛心顿平而就简策。则未死前馀日几何。以是猛省起来。稍有片暇。辄以披阅为事。自去月看朱子大全书部。驰涉几了。兼看大学。草草数番则过。方到诚意章。觉有大疑端。所谓自欺云者。语类中凡有两般说。欠了分数。半知半不知。以此为自欺者。最为斑斑。末后一说。则直以小人闲居为自欺。其所释自欺意义。只是就欺人中。略分先后表里之势。便谓如是释去。方贴于文义。未知经义果如此否。而章句之合于何说。亦难详。未知高明寻常看得如何。离索久矣。聊此发端。以开讲评之路。想亦不厌反复也。馀不宣。
与鱼有凤
昌翕家祸荐酷。仲母奄又弃背。孤露残命。靡所依庇。痛苦摧裂。不自堪忍。奈何奈何。且日月有时。亡妻葬期定矣。念其存日糟糠不厌。而惟穷阨流离是饱。半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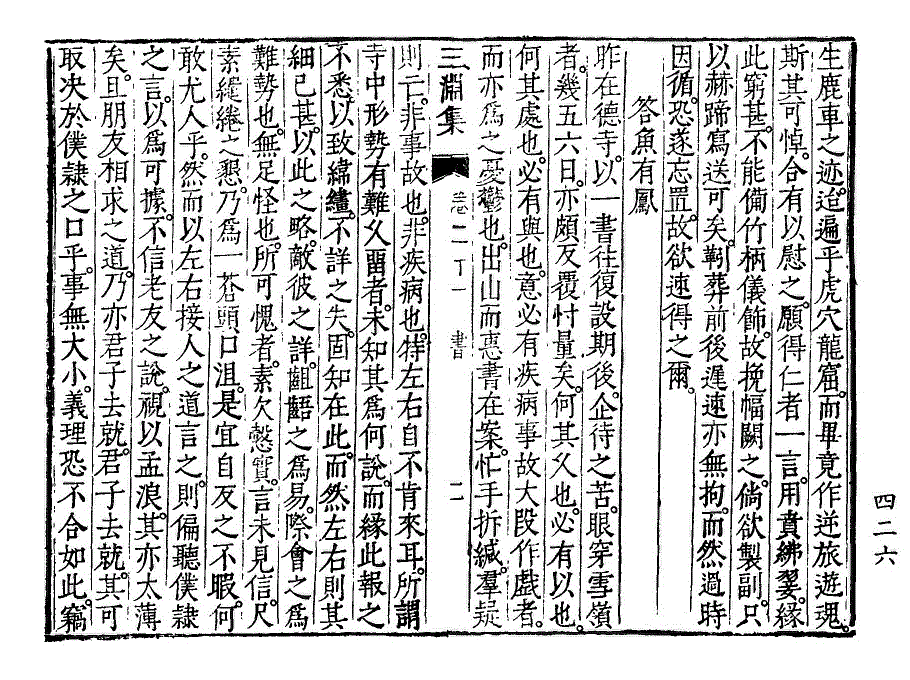 生鹿车之迹。迨遍乎虎穴龙窟。而毕竟作逆旅游魂。斯其可悼。合有以慰之。愿得仁者一言。用贲绋翣。缘此穷甚。不能备竹柄仪饰。故挽幅阙之。倘欲制副。只以赫蹄写送可矣。靷葬前后迟速亦无拘。而然过时因循。恐遂忘置。故欲速得之尔。
生鹿车之迹。迨遍乎虎穴龙窟。而毕竟作逆旅游魂。斯其可悼。合有以慰之。愿得仁者一言。用贲绋翣。缘此穷甚。不能备竹柄仪饰。故挽幅阙之。倘欲制副。只以赫蹄写送可矣。靷葬前后迟速亦无拘。而然过时因循。恐遂忘置。故欲速得之尔。答鱼有凤
昨在德寺。以一书往复设期后。企待之苦。眼穿雪岭者。几五六日。亦颇反覆忖量矣。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意必有疾病事故大段作戏者。而亦为之忧郁也。出山而惠书在案。忙手拆缄。群疑则亡。非事故也。非疾病也。特左右自不肯来耳。所谓寺中形势有难久留者。未知其为何说。而缘此报之不悉。以致纬繣。不详之失。固知在此。而然左右则其细已甚。以此之略。敌彼之详。龃龉之为易。际会之为难势也。无足怪也。所可愧者。素欠悫实。言未见信。尺素缱绻之恳。乃为一苍头口沮。是宜自反之不暇。何敢尤人乎。然而以左右接人之道言之。则偏听仆隶之言。以为可据。不信老友之说。视以孟浪。其亦太薄矣。且朋友相求之道。乃亦君子去就。君子去就。其可取决于仆隶之口乎。事无大小。义理恐不合如此。窃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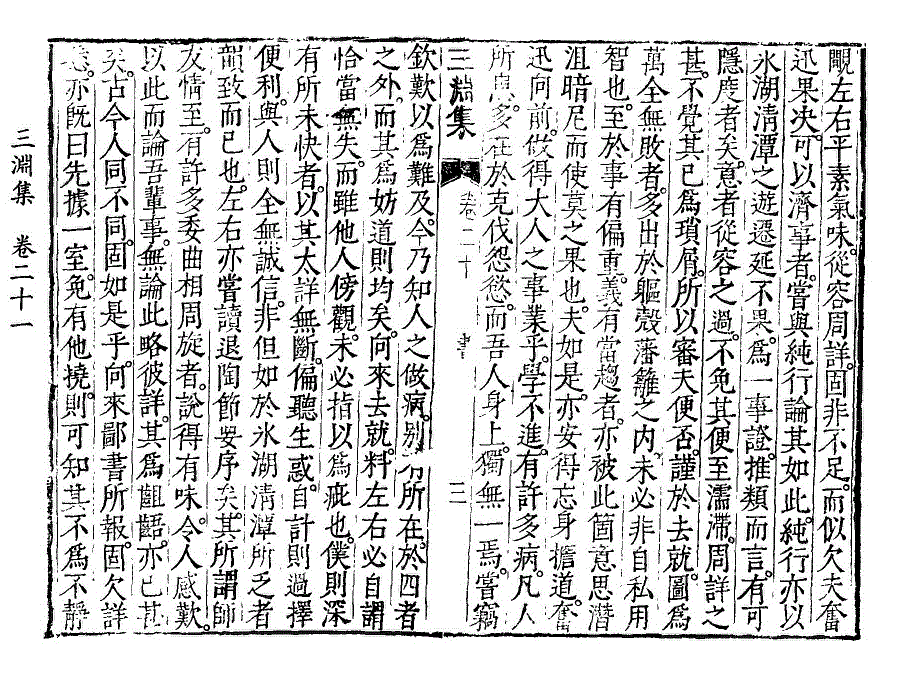 覵左右平素气味。从容周详。固非不足。而似欠夫奋迅果决。可以济事者。尝与纯行论其如此。纯行亦以冰湖清潭之游迁延不果。为一事證。推类而言。有可隐度者矣。意者从容之过。不免其便至濡滞。周详之甚。不觉其已为琐屑。所以审夫便否。谨于去就。图为万全无败者。多出于躯壳藩篱之内。未必非自私用智也。至于事有偏重。义有当趋者。亦被此个意思潜沮暗尼而使莫之果也。夫如是。亦安得忘身担道。奋迅向前。做得大人之事业乎。学不进。有许多病。凡人所患。多在于克伐怨欲。而吾人身上。独无一焉。尝窃钦叹以为难及。今乃知人之做病。别有所在。于四者之外。而其为妨道则均矣。向来去就。料左右必自谓恰当无失。而虽他人傍观。未必指以为疵也。仆则深有所未快者。以其太详无断。偏听生惑。自计则过择便利。与人则全无诚信。非但如于冰湖清潭所乏者韵致而已也。左右亦尝读退陶节要序矣。其所谓师友情至。有许多委曲相周旋者。说得有味。令人感叹。以此而论吾辈事。无论此略彼详。其为龃龉。亦已甚矣。古今人同不同。固如是乎。向来鄙书所报。固欠详悉。亦既曰先据一室。免有他挠。则可知其不为不静
覵左右平素气味。从容周详。固非不足。而似欠夫奋迅果决。可以济事者。尝与纯行论其如此。纯行亦以冰湖清潭之游迁延不果。为一事證。推类而言。有可隐度者矣。意者从容之过。不免其便至濡滞。周详之甚。不觉其已为琐屑。所以审夫便否。谨于去就。图为万全无败者。多出于躯壳藩篱之内。未必非自私用智也。至于事有偏重。义有当趋者。亦被此个意思潜沮暗尼而使莫之果也。夫如是。亦安得忘身担道。奋迅向前。做得大人之事业乎。学不进。有许多病。凡人所患。多在于克伐怨欲。而吾人身上。独无一焉。尝窃钦叹以为难及。今乃知人之做病。别有所在。于四者之外。而其为妨道则均矣。向来去就。料左右必自谓恰当无失。而虽他人傍观。未必指以为疵也。仆则深有所未快者。以其太详无断。偏听生惑。自计则过择便利。与人则全无诚信。非但如于冰湖清潭所乏者韵致而已也。左右亦尝读退陶节要序矣。其所谓师友情至。有许多委曲相周旋者。说得有味。令人感叹。以此而论吾辈事。无论此略彼详。其为龃龉。亦已甚矣。古今人同不同。固如是乎。向来鄙书所报。固欠详悉。亦既曰先据一室。免有他挠。则可知其不为不静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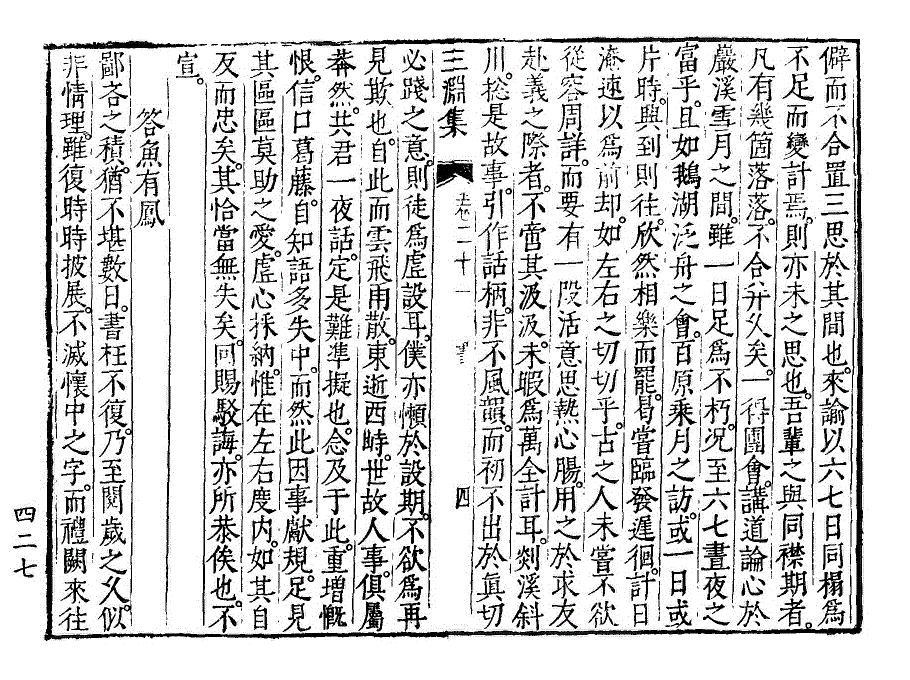 僻而不合置三思于其间也。来谕以六七日同榻为不足而变计焉。则亦未之思也。吾辈之与同襟期者。凡有几个落落。不合并久矣。一得团会。讲道论心于岩溪雪月之间。虽一日足为不朽。况至六七昼夜之富乎。且如鹅湖泛舟之会。百原乘月之访。或一日或片时。兴到则往。欣然相乐而罢。曷尝临发迟徊。计日淹速以为前却。如左右之切切乎。古之人未尝不欲从容周详。而要有一段活意思热心肠。用之于求友赴义之际者。不啻其汲汲。未暇为万全计耳。剡溪斜川。总是故事。引作话柄。非不风韵。而初不出于真切必践之意。则徒为虚设耳。仆亦懒于设期。不欲为再见欺也。自此而云飞雨散。东逝西峙。世故人事。俱属莽然。共君一夜话。定是难准拟也。念及于此。重增慨恨。信口葛藤。自知语多失中。而然此因事献规。足见其区区莫助之爱。虚心采纳。惟在左右度内。如其自反而忠矣。其恰当无失矣。回赐驳诲。亦所恭俟也。不宣。
僻而不合置三思于其间也。来谕以六七日同榻为不足而变计焉。则亦未之思也。吾辈之与同襟期者。凡有几个落落。不合并久矣。一得团会。讲道论心于岩溪雪月之间。虽一日足为不朽。况至六七昼夜之富乎。且如鹅湖泛舟之会。百原乘月之访。或一日或片时。兴到则往。欣然相乐而罢。曷尝临发迟徊。计日淹速以为前却。如左右之切切乎。古之人未尝不欲从容周详。而要有一段活意思热心肠。用之于求友赴义之际者。不啻其汲汲。未暇为万全计耳。剡溪斜川。总是故事。引作话柄。非不风韵。而初不出于真切必践之意。则徒为虚设耳。仆亦懒于设期。不欲为再见欺也。自此而云飞雨散。东逝西峙。世故人事。俱属莽然。共君一夜话。定是难准拟也。念及于此。重增慨恨。信口葛藤。自知语多失中。而然此因事献规。足见其区区莫助之爱。虚心采纳。惟在左右度内。如其自反而忠矣。其恰当无失矣。回赐驳诲。亦所恭俟也。不宣。答鱼有凤
鄙吝之积。犹不堪数日。书枉不复。乃至阅岁之久。似非情理。虽复时时披展。不灭怀中之字。而礼阙来往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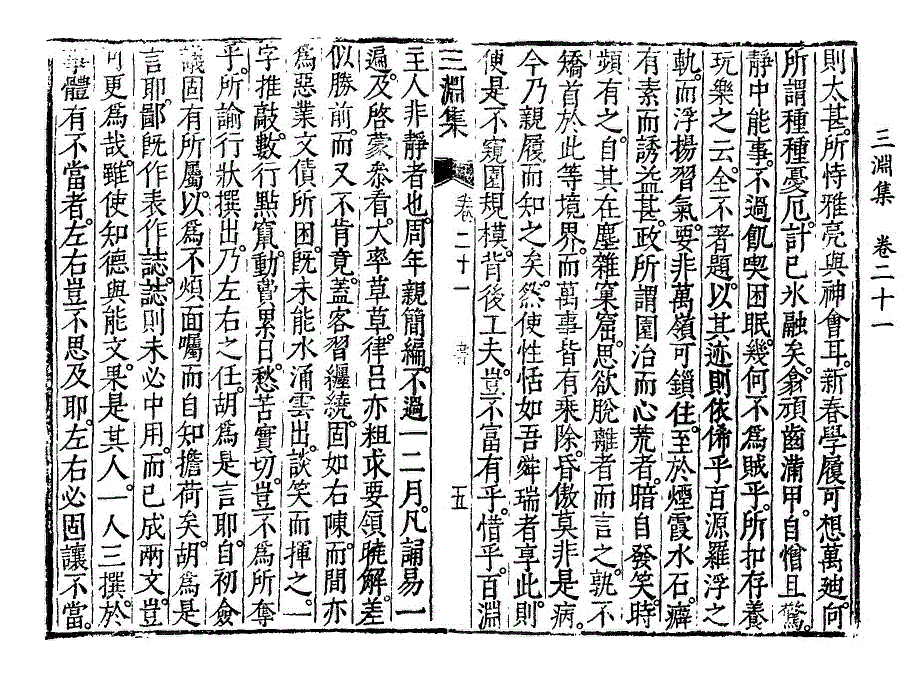 则太甚。所恃雅亮与神会耳。新春学履可想万迪。向所谓种种忧厄。计已冰融矣。翕顽齿满甲。自憎且惊。静中能事。不过饥吃困眠。几何不为贼乎。所扣存养玩乐之云。全不著题。以其迹则依俙乎百源罗浮之轨。而浮扬习气。要非万岭可锁住。至于烟霞水石。癖有素而诱益甚。政所谓园治而心荒者。暗自发笑。时频有之。自其在尘杂窠窟。思欲脱离者而言之。孰不矫首于此等境界。而万事皆有乘除。昏傲莫非是病。今乃亲履而知之矣。然使性恬如吾舜瑞者享此。则便是不窥园规模。背后工夫。岂不富有乎。惜乎。百渊主人非静者也。周年亲简编。不过一二月。凡诵易一遍。及启蒙参看。大率草草。律吕亦粗求要领晓解。差似胜前。而又不肯竟。盖客习缠绕。固如右陈。而间亦为恶业文债所困。既未能水涌云出。谈笑而挥之。一字推敲。数行点窜。动费累日。愁苦实切。岂不为所夺乎。所谕行状撰出。乃左右之任。胡为是言耶。自初佥议固有所属。以为不烦面嘱而自知担荷矣。胡为是言耶。鄙既作表作志。志则未必中用。而已成两文。岂可更为哉。虽使知德与能文。果是其人。一人三撰。于事体有不当者。左右岂不思及耶。左右必固让不当。
则太甚。所恃雅亮与神会耳。新春学履可想万迪。向所谓种种忧厄。计已冰融矣。翕顽齿满甲。自憎且惊。静中能事。不过饥吃困眠。几何不为贼乎。所扣存养玩乐之云。全不著题。以其迹则依俙乎百源罗浮之轨。而浮扬习气。要非万岭可锁住。至于烟霞水石。癖有素而诱益甚。政所谓园治而心荒者。暗自发笑。时频有之。自其在尘杂窠窟。思欲脱离者而言之。孰不矫首于此等境界。而万事皆有乘除。昏傲莫非是病。今乃亲履而知之矣。然使性恬如吾舜瑞者享此。则便是不窥园规模。背后工夫。岂不富有乎。惜乎。百渊主人非静者也。周年亲简编。不过一二月。凡诵易一遍。及启蒙参看。大率草草。律吕亦粗求要领晓解。差似胜前。而又不肯竟。盖客习缠绕。固如右陈。而间亦为恶业文债所困。既未能水涌云出。谈笑而挥之。一字推敲。数行点窜。动费累日。愁苦实切。岂不为所夺乎。所谕行状撰出。乃左右之任。胡为是言耶。自初佥议固有所属。以为不烦面嘱而自知担荷矣。胡为是言耶。鄙既作表作志。志则未必中用。而已成两文。岂可更为哉。虽使知德与能文。果是其人。一人三撰。于事体有不当者。左右岂不思及耶。左右必固让不当。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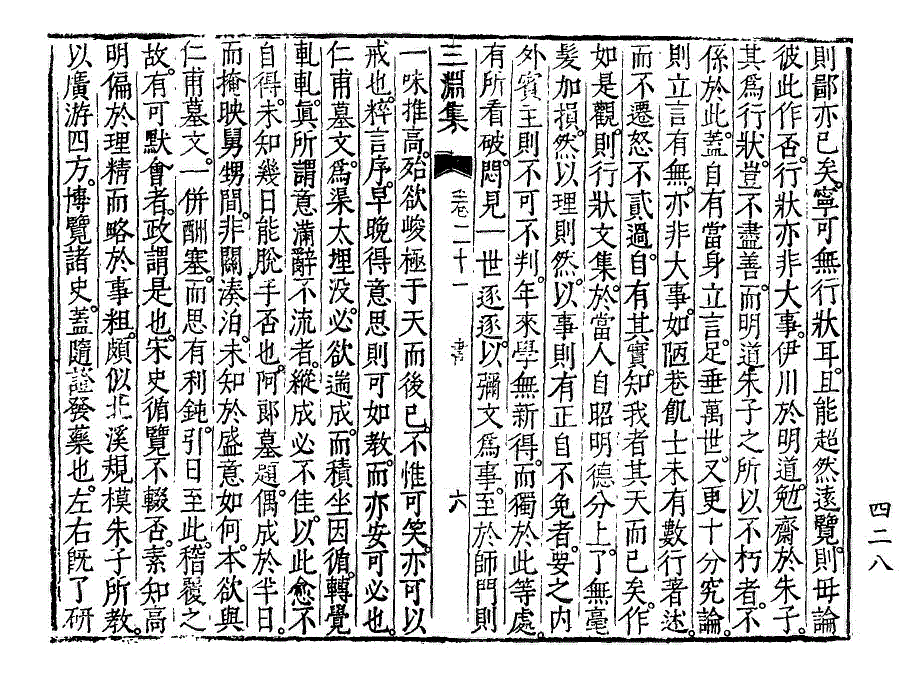 则鄙亦已矣。宁可无行状耳。且能超然远览。则毋论彼此作否。行状亦非大事。伊川于明道。勉斋于朱子。其为行状。岂不尽善。而明道,朱子之所以不朽者。不系于此。盖自有当身立言。足垂万世。又更十分究论。则立言有无。亦非大事。如陋巷饥士未有数行著述。而不迁怒不贰过。自有其实。知我者其天而已矣。作如是观。则行状文集。于当人自昭明德分上。了无毫发加损。然以理则然。以事则有正自不免者。要之内外宾主则不可不判。年来学无新得。而独于此等处。有所看破。闷见一世逐逐。以弥文为事。至于师门则一味推高。殆欲峻极于天而后已。不惟可笑。亦可以戒也。粹言序。早晚得意思则可如教。而亦安可必也。仁甫墓文。为渠太埋没。必欲遄成。而积坐因循。转觉轧轧。真所谓意满辞不流者。纵成必不佳。以此愈不自得。未知几日能脱手否也。阿郎墓题。偶成于半日。而掩映舅甥间。非关凑泊。未知于盛意如何。本欲与仁甫墓文。一并酬塞。而思有利钝。引日至此。稽覆之故。有可默会者。政谓是也。宋史循览不辍否。素知高明偏于理精而略于事粗。颇似北溪规模朱子所教。以广游四方。博览诸史。盖随證发药也。左右既了研
则鄙亦已矣。宁可无行状耳。且能超然远览。则毋论彼此作否。行状亦非大事。伊川于明道。勉斋于朱子。其为行状。岂不尽善。而明道,朱子之所以不朽者。不系于此。盖自有当身立言。足垂万世。又更十分究论。则立言有无。亦非大事。如陋巷饥士未有数行著述。而不迁怒不贰过。自有其实。知我者其天而已矣。作如是观。则行状文集。于当人自昭明德分上。了无毫发加损。然以理则然。以事则有正自不免者。要之内外宾主则不可不判。年来学无新得。而独于此等处。有所看破。闷见一世逐逐。以弥文为事。至于师门则一味推高。殆欲峻极于天而后已。不惟可笑。亦可以戒也。粹言序。早晚得意思则可如教。而亦安可必也。仁甫墓文。为渠太埋没。必欲遄成。而积坐因循。转觉轧轧。真所谓意满辞不流者。纵成必不佳。以此愈不自得。未知几日能脱手否也。阿郎墓题。偶成于半日。而掩映舅甥间。非关凑泊。未知于盛意如何。本欲与仁甫墓文。一并酬塞。而思有利钝。引日至此。稽覆之故。有可默会者。政谓是也。宋史循览不辍否。素知高明偏于理精而略于事粗。颇似北溪规模朱子所教。以广游四方。博览诸史。盖随證发药也。左右既了研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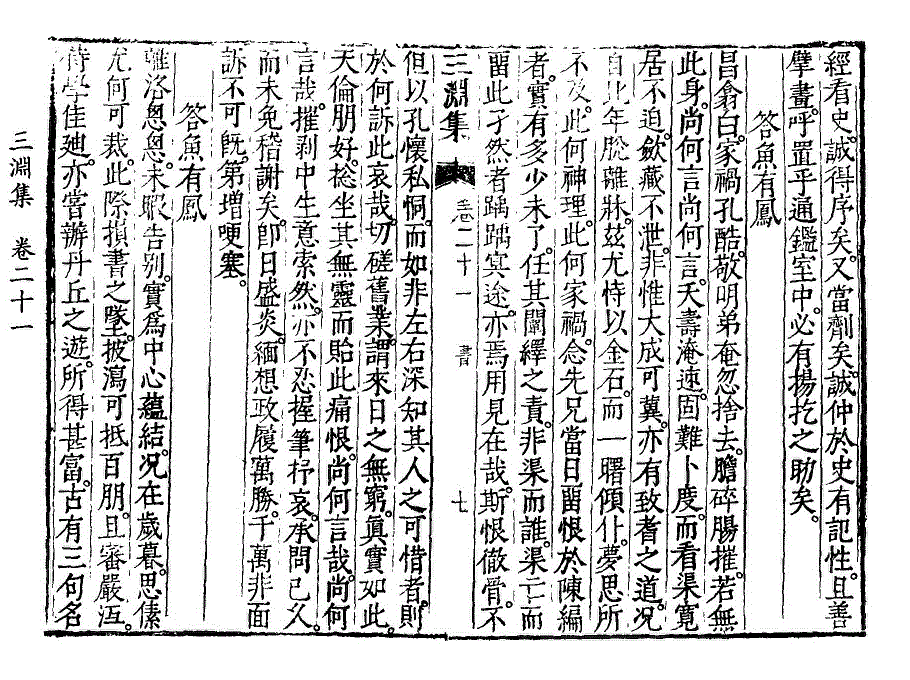 经看史。诚得序矣。又当剂矣。诚仲于史有记性。且善擘画。呼置乎通鉴室中。必有扬扢之助矣。
经看史。诚得序矣。又当剂矣。诚仲于史有记性。且善擘画。呼置乎通鉴室中。必有扬扢之助矣。答鱼有凤
昌翕白。家祸孔酷。敬明弟奄忽舍去。胆碎肠摧。若无此身。尚何言尚何言。夭寿淹速。固难卜度。而看渠宽居不迫。敛藏不泄。非惟大成可冀。亦有致耆之道。况自比年脱离床。玆尤恃以金石。而一曙倾仆。梦思所不及。此何神理。此何家祸。念先兄当日留恨于陈编者。实有多少未了。任其阐绎之责。非渠而谁。渠亡而留此孑然者踽踽冥途。亦焉用见在哉。斯恨彻骨。不但以孔怀私恫。而如非左右深知其人之可惜者。则于何诉此哀哉。切磋旧业。谓来日之无穷。真实如此。天伦朋好。总坐其无灵而贻此痛恨。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摧剥中生意索然。亦不忍握笔抒哀。承问已久。而未免稽谢矣。即日盛炎。缅想政履万胜。千万非面诉不可既。第增哽塞。
答鱼有凤
离洛悤悤。未暇告别。实为中心蕴结。况在岁暮。思傃尤何可裁。此际损书之坠。披泻可抵百朋。且审严冱。侍学佳迪。亦尝办丹丘之游。所得甚富。古有三句名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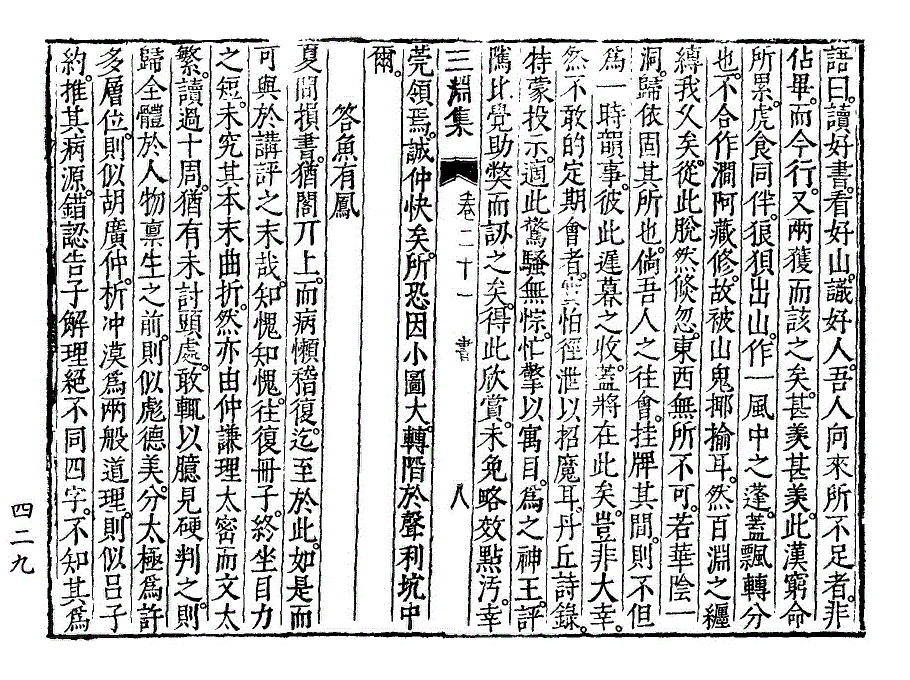 语曰。读好书。看好山。识好人。吾人向来所不足者。非佔毕。而今行。又两获而该之矣。甚羡甚羡。此汉穷命所累。虎食同伴。狼狈出山。作一风中之蓬。盖飘转分也。不合作涧阿藏修。故被山鬼揶揄耳。然百渊之缠缚我久矣。从此脱然倏忽。东西无所不可。若华阴一洞。归依固其所也。倘吾人之往会。挂牌其间。则不但为一时韵事。彼此迟暮之收。盖将在此矣。岂非大幸。然不敢的定期会者。实怕径泄以招魔耳。丹丘诗录。特蒙投示。适此惊骚无悰。忙擎以寓目。为之神王。评骘比觉助弊而讱之矣。得此欣赏。未免略效点污。幸莞领焉。诚仲快矣。所恐因小图大。转陷于声利坑中尔。
语曰。读好书。看好山。识好人。吾人向来所不足者。非佔毕。而今行。又两获而该之矣。甚羡甚羡。此汉穷命所累。虎食同伴。狼狈出山。作一风中之蓬。盖飘转分也。不合作涧阿藏修。故被山鬼揶揄耳。然百渊之缠缚我久矣。从此脱然倏忽。东西无所不可。若华阴一洞。归依固其所也。倘吾人之往会。挂牌其间。则不但为一时韵事。彼此迟暮之收。盖将在此矣。岂非大幸。然不敢的定期会者。实怕径泄以招魔耳。丹丘诗录。特蒙投示。适此惊骚无悰。忙擎以寓目。为之神王。评骘比觉助弊而讱之矣。得此欣赏。未免略效点污。幸莞领焉。诚仲快矣。所恐因小图大。转陷于声利坑中尔。答鱼有凤
夏间损书。犹阁丌上。而病懒稽复。迄至于此。如是而可与于讲评之末哉。知愧知愧。往复册子。终坐目力之短。未究其本末曲折。然亦由仲谦理太密而文太繁。读过十周。犹有未讨头处。敢辄以臆见硬判之。则归全体于人物禀生之前。则似彪德美。分太极为许多层位。则似胡广仲。析冲漠为两般道理。则似吕子约。推其病源。错认告子解理绝不同四字。不知其为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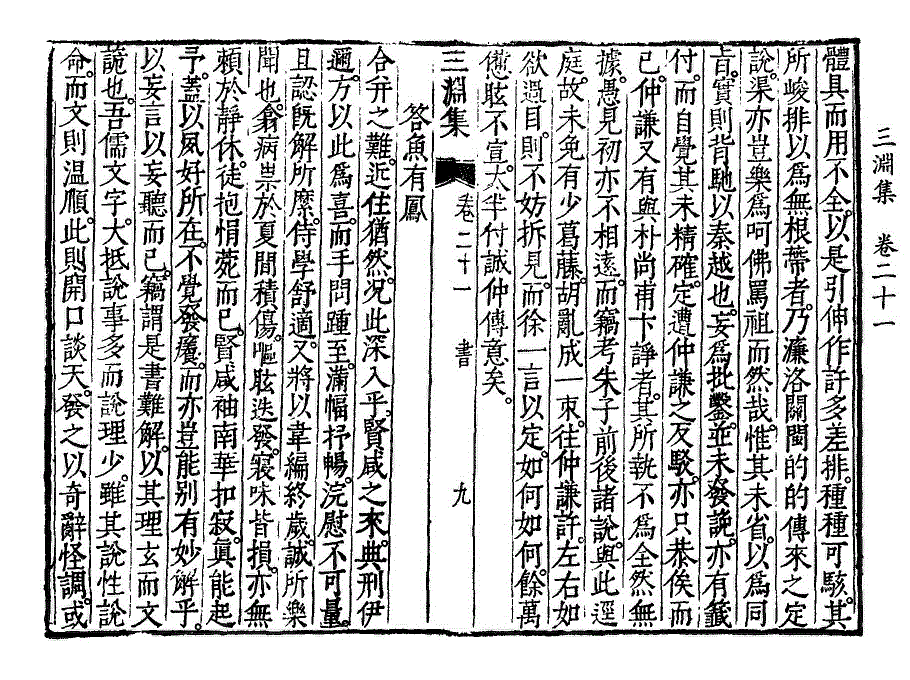 体具而用不全。以是引伸作许多差排。种种可骇。其所峻排以为无根蒂者。乃濂洛关闽的的传来之定说。渠亦岂乐为呵佛骂祖而然哉。惟其未省。以为同旨。实则背驰以秦越也。妄为批凿。并未发说。亦有签付。而自觉其未精确。定遭仲谦之反驳。亦只恭俟而已。仲谦又有与朴尚甫卞诤者。其所执不为全然无据。愚见初亦不相远。而窃考朱子前后诸说。与此径庭。故未免有少葛藤。胡乱成一束。往仲谦许。左右如欲过目。则不妨拆见。而徐一言以定。如何如何。馀万惫眩不宣。太半付诚仲传意矣。
体具而用不全。以是引伸作许多差排。种种可骇。其所峻排以为无根蒂者。乃濂洛关闽的的传来之定说。渠亦岂乐为呵佛骂祖而然哉。惟其未省。以为同旨。实则背驰以秦越也。妄为批凿。并未发说。亦有签付。而自觉其未精确。定遭仲谦之反驳。亦只恭俟而已。仲谦又有与朴尚甫卞诤者。其所执不为全然无据。愚见初亦不相远。而窃考朱子前后诸说。与此径庭。故未免有少葛藤。胡乱成一束。往仲谦许。左右如欲过目。则不妨拆见。而徐一言以定。如何如何。馀万惫眩不宣。太半付诚仲传意矣。答鱼有凤
合并之难。近住犹然。况此深入乎。贤咸之来。典刑伊迩。方以此为喜。而手问踵至。满幅抒畅。浣慰不可量。且认既解所縻。侍学舒适。又将以韦编终岁。诚所乐闻也。翕病祟于夏间积伤。呕眩迭发。寝味皆损。亦无赖于静休。徒抱悁菀而已。贤咸袖南华扣寂。真能起予。盖以夙好所在。不觉发痒。而亦岂能别有妙解乎。以妄言以妄听而已。窃谓是书难解。以其理玄而文诡也。吾儒文字。大抵说事多而说理少。虽其说性说命。而文则温顺。此则开口谈天。发之以奇辞怪调。或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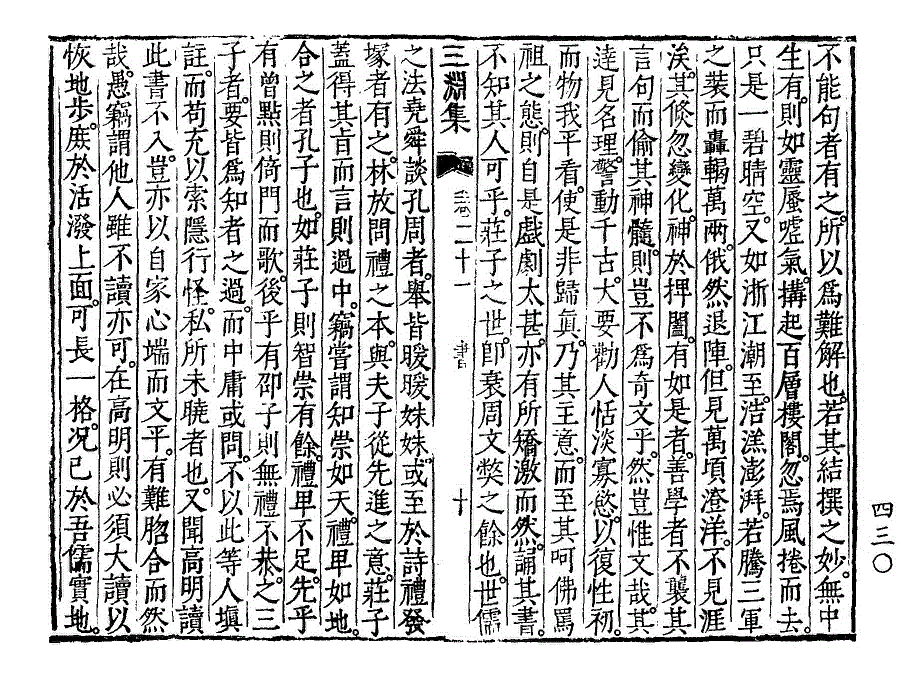 不能句者有之。所以为难解也。若其结撰之妙。无中生有。则如灵蜃嘘气。搆起百层楼阁。忽焉风捲而去。只是一碧晴空。又如浙江潮至。浩溔澎湃。若腾三军之装而轰轕万两。俄然退阵。但见万顷澄洋。不见涯涘。其倏忽变化。神于捭阖。有如是者。善学者不袭其言句而偷其神髓。则岂不为奇文乎。然岂惟文哉。其达见名理。警动千古。大要劝人恬淡寡欲。以复性初。而物我平看。使是非归真。乃其主意。而至其呵佛骂祖之态。则自是戏剧太甚。亦有所矫激而然。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庄子之世。即衰周文弊之馀也。世儒之法尧舜谈孔周者。举皆暖暖姝姝。或至于诗礼发冢者有之。林放问礼之本。与夫子从先进之意。庄子盖得其旨而言则过中。窃尝谓知崇如天。礼卑如地。合之者孔子也。如庄子则智崇有馀。礼卑不足。先乎有曾点则倚门而歌。后乎有邵子则无礼不恭。之三子者。要皆为知者之过。而中庸或问。不以此等人填注。而苟充以索隐行怪。私所未晓者也。又闻高明读此书不入。岂亦以自家心端而文平。有难吻合而然哉。愚窃谓他人虽不读亦可。在高明则必须大读以恢地步。庶于活泼上面。可长一格。况已于吾儒实地。
不能句者有之。所以为难解也。若其结撰之妙。无中生有。则如灵蜃嘘气。搆起百层楼阁。忽焉风捲而去。只是一碧晴空。又如浙江潮至。浩溔澎湃。若腾三军之装而轰轕万两。俄然退阵。但见万顷澄洋。不见涯涘。其倏忽变化。神于捭阖。有如是者。善学者不袭其言句而偷其神髓。则岂不为奇文乎。然岂惟文哉。其达见名理。警动千古。大要劝人恬淡寡欲。以复性初。而物我平看。使是非归真。乃其主意。而至其呵佛骂祖之态。则自是戏剧太甚。亦有所矫激而然。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庄子之世。即衰周文弊之馀也。世儒之法尧舜谈孔周者。举皆暖暖姝姝。或至于诗礼发冢者有之。林放问礼之本。与夫子从先进之意。庄子盖得其旨而言则过中。窃尝谓知崇如天。礼卑如地。合之者孔子也。如庄子则智崇有馀。礼卑不足。先乎有曾点则倚门而歌。后乎有邵子则无礼不恭。之三子者。要皆为知者之过。而中庸或问。不以此等人填注。而苟充以索隐行怪。私所未晓者也。又闻高明读此书不入。岂亦以自家心端而文平。有难吻合而然哉。愚窃谓他人虽不读亦可。在高明则必须大读以恢地步。庶于活泼上面。可长一格。况已于吾儒实地。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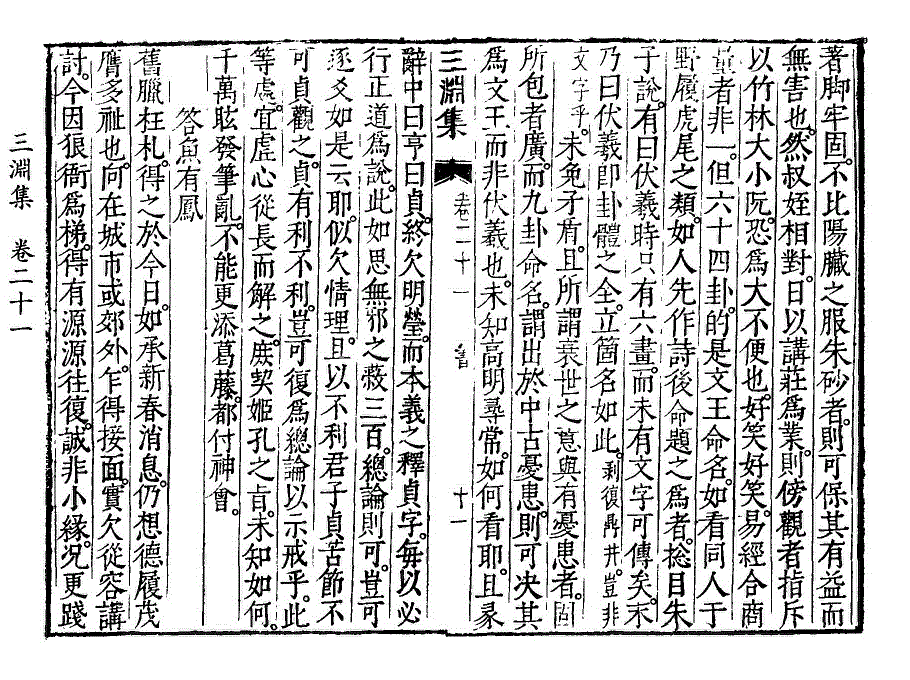 著脚牢固。不比阳脏之服朱砂者。则可保其有益而无害也。然叔侄相对。日以讲庄为业。则傍观者指斥以竹林大小阮。恐为大不便也。好笑好笑。易经合商量者非一。但六十四卦。的是文王命名。如看同人于野履虎尾之类。如人先作诗后命题之为者。总目朱子说。有曰伏羲时只有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矣。末乃曰伏羲即卦体之全。立个名如此。(剥复鼎井。岂非文字乎。)未免矛盾。且所谓衰世之意与有忧患者。固所包者广。而九卦命名。谓出于中古忧患。则可决其为文王而非伏羲也。未知高明寻常。如何看耶。且彖辞中曰亨曰贞。终欠明莹。而本义之释贞字。每以必行正道为说。此如思无邪之蔽三百。总论则可。岂可逐爻如是云耶。似欠情理。且以不利君子贞苦节不可贞观之。贞有利不利。岂可复为总论以示戒乎。此等处。宜虚心从长而解之。庶契姬孔之旨。未知如何。千万眩发笔乱。不能更添葛藤。都付神会。
著脚牢固。不比阳脏之服朱砂者。则可保其有益而无害也。然叔侄相对。日以讲庄为业。则傍观者指斥以竹林大小阮。恐为大不便也。好笑好笑。易经合商量者非一。但六十四卦。的是文王命名。如看同人于野履虎尾之类。如人先作诗后命题之为者。总目朱子说。有曰伏羲时只有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矣。末乃曰伏羲即卦体之全。立个名如此。(剥复鼎井。岂非文字乎。)未免矛盾。且所谓衰世之意与有忧患者。固所包者广。而九卦命名。谓出于中古忧患。则可决其为文王而非伏羲也。未知高明寻常。如何看耶。且彖辞中曰亨曰贞。终欠明莹。而本义之释贞字。每以必行正道为说。此如思无邪之蔽三百。总论则可。岂可逐爻如是云耶。似欠情理。且以不利君子贞苦节不可贞观之。贞有利不利。岂可复为总论以示戒乎。此等处。宜虚心从长而解之。庶契姬孔之旨。未知如何。千万眩发笔乱。不能更添葛藤。都付神会。答鱼有凤
旧腊枉札。得之于今日。如承新春消息。仍想德履茂膺多祉也。向在城市或郊外。乍得接面。实欠从容讲讨。今因狼衙为梯。得有源源往复。诚非小缘。况更践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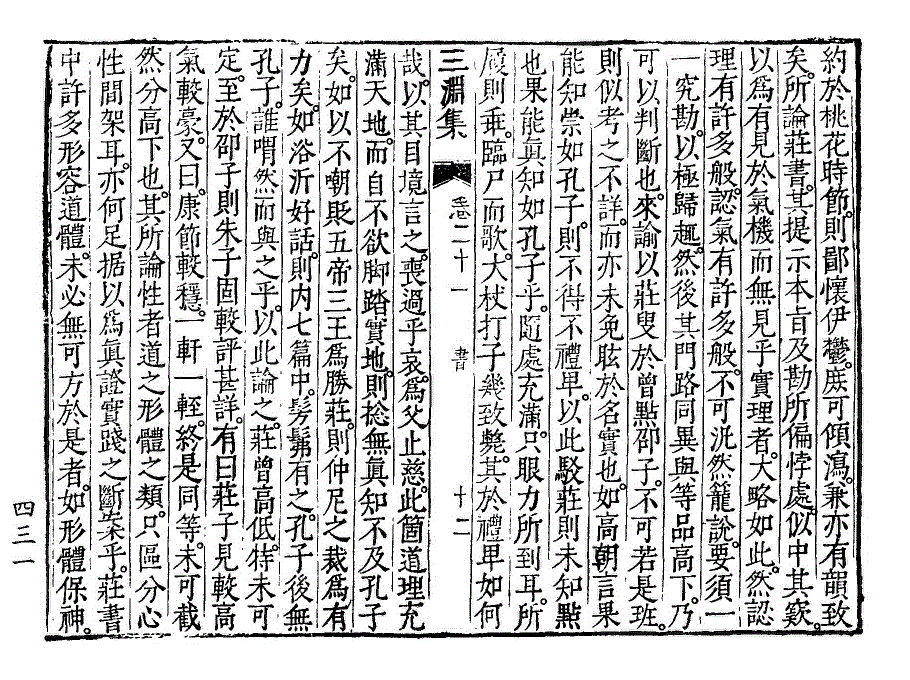 约于桃花时节。则鄙怀伊郁。庶可倾泻。兼亦有韵致矣。所论庄书。其提示本旨及勘所偏悖处。似中其窾。以为有见于气机而无见乎实理者。大略如此。然认理有许多般。认气有许多般。不可汎然笼说。要须一一究勘。以极归趣。然后其门路同异与等品高下。乃可以判断也。来谕以庄叟于曾点邵子。不可若是班。则似考之不详。而亦未免眩于名实也。如高朝言果能知崇如孔子。则不得不礼卑。以此驳庄则未知点也果能真知如孔子乎。随处充满。只眼力所到耳。所履则乖。临尸而歌。大杖打子几致毙。其于礼卑如何哉。以其目境言之。丧过乎哀。为父止慈。此个道理充满天地。而自不欲脚踏实地。则总无真知不及孔子矣。如以不嘲贬五帝三王为胜庄。则仲尼之裁为有力矣。如浴沂好话。则内七篇中。髣髴有之。孔子后无孔子。谁喟然而与之乎。以此论之。庄曾高低。特未可定。至于邵子则朱子固较评甚详。有曰庄子见较高气较豪。又曰。康节较稳。一轩一轾。终是同等。未可截然分高下也。其所论性者道之形体之类。只区分心性间架耳。亦何足据以为真證实践之断案乎。庄书中许多形容道体。未必无可方于是者。如形体保神。
约于桃花时节。则鄙怀伊郁。庶可倾泻。兼亦有韵致矣。所论庄书。其提示本旨及勘所偏悖处。似中其窾。以为有见于气机而无见乎实理者。大略如此。然认理有许多般。认气有许多般。不可汎然笼说。要须一一究勘。以极归趣。然后其门路同异与等品高下。乃可以判断也。来谕以庄叟于曾点邵子。不可若是班。则似考之不详。而亦未免眩于名实也。如高朝言果能知崇如孔子。则不得不礼卑。以此驳庄则未知点也果能真知如孔子乎。随处充满。只眼力所到耳。所履则乖。临尸而歌。大杖打子几致毙。其于礼卑如何哉。以其目境言之。丧过乎哀。为父止慈。此个道理充满天地。而自不欲脚踏实地。则总无真知不及孔子矣。如以不嘲贬五帝三王为胜庄。则仲尼之裁为有力矣。如浴沂好话。则内七篇中。髣髴有之。孔子后无孔子。谁喟然而与之乎。以此论之。庄曾高低。特未可定。至于邵子则朱子固较评甚详。有曰庄子见较高气较豪。又曰。康节较稳。一轩一轾。终是同等。未可截然分高下也。其所论性者道之形体之类。只区分心性间架耳。亦何足据以为真證实践之断案乎。庄书中许多形容道体。未必无可方于是者。如形体保神。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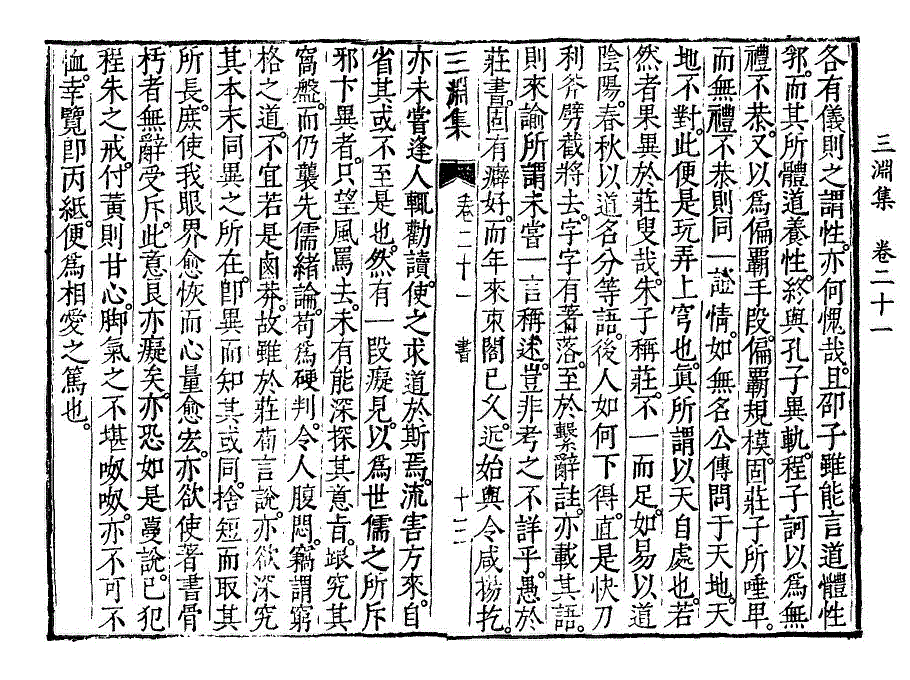 各有仪则之谓性。亦何愧哉。且邵子虽能言道体性郛。而其所体道养性。终与孔子异轨。程子诃以为无礼不恭。又以为偏霸手段。偏霸规模。固庄子所唾卑。而无礼不恭则同一證情。如无名公传问于天地。天地不对。此便是玩弄上穹也。真所谓以天自处也。若然者果异于庄叟哉。朱子称庄。不一而足。如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人如何下得。直是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著落。至于系辞注。亦载其语。则来谕所谓未尝一言称述。岂非考之不详乎。愚于庄书。固有癖好。而年来束阁已久。近始与令咸扬扢。亦未尝逢人辄劝读。使之求道于斯焉。流害方来。自省其或不至是也。然有一段痴见。以为世儒之所斥邪卞异者。只望风骂去。未有能深探其意旨。跟究其窝盘。而仍袭先儒绪论。苟为硬判。令人腹闷。窃谓穷格之道。不宜若是卤莽。故虽于庄荀言说。亦欲深究其本末同异之所在。即异而知其或同。舍短而取其所长。庶使我眼界愈恢而心量愈宏。亦欲使著书骨朽者无辞受斥。此意良亦痴矣。亦恐如是蔓说。已犯程朱之戒。付黄则甘心。脚气之不堪呶呶。亦不可不恤。幸览即丙纸。便为相爱之笃也。
各有仪则之谓性。亦何愧哉。且邵子虽能言道体性郛。而其所体道养性。终与孔子异轨。程子诃以为无礼不恭。又以为偏霸手段。偏霸规模。固庄子所唾卑。而无礼不恭则同一證情。如无名公传问于天地。天地不对。此便是玩弄上穹也。真所谓以天自处也。若然者果异于庄叟哉。朱子称庄。不一而足。如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人如何下得。直是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著落。至于系辞注。亦载其语。则来谕所谓未尝一言称述。岂非考之不详乎。愚于庄书。固有癖好。而年来束阁已久。近始与令咸扬扢。亦未尝逢人辄劝读。使之求道于斯焉。流害方来。自省其或不至是也。然有一段痴见。以为世儒之所斥邪卞异者。只望风骂去。未有能深探其意旨。跟究其窝盘。而仍袭先儒绪论。苟为硬判。令人腹闷。窃谓穷格之道。不宜若是卤莽。故虽于庄荀言说。亦欲深究其本末同异之所在。即异而知其或同。舍短而取其所长。庶使我眼界愈恢而心量愈宏。亦欲使著书骨朽者无辞受斥。此意良亦痴矣。亦恐如是蔓说。已犯程朱之戒。付黄则甘心。脚气之不堪呶呶。亦不可不恤。幸览即丙纸。便为相爱之笃也。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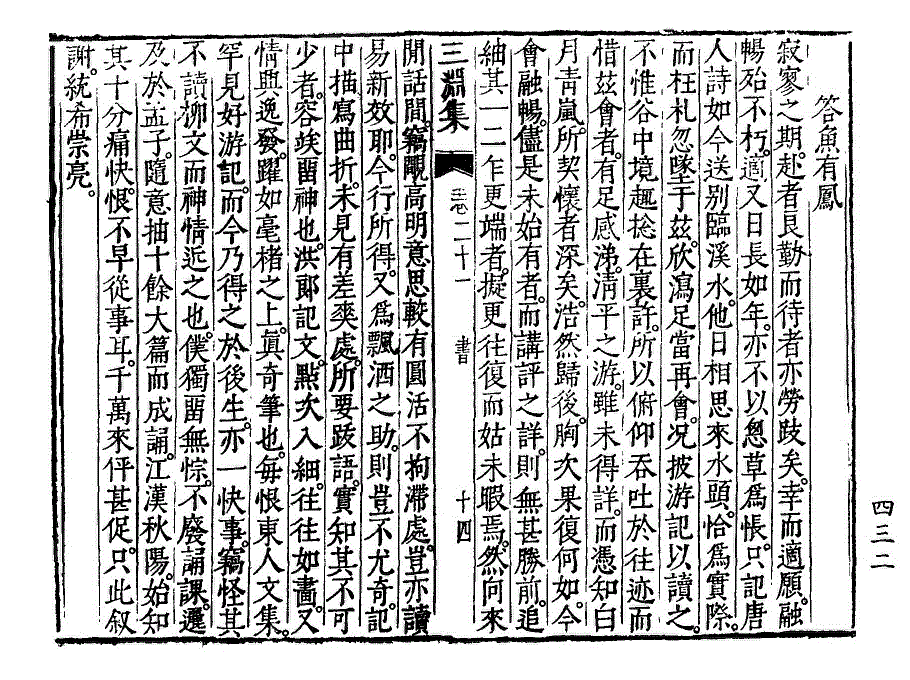 答鱼有凤
答鱼有凤寂寥之期。赴者良勤而待者亦劳跂矣。幸而适愿。融畅殆不朽。适又日长如年。亦不以悤草为怅。只记唐人诗如今送别临溪水。他日相思来水头。恰为实际。而枉札忽坠于玆。欣泻足当再会。况披游记以读之。不惟谷中境趣总在里许。所以俯仰吞吐于往迹而惜玆会者。有足感涕。清平之游。虽未得详。而凭知白月青岚。所契怀者深矣。浩然归后。胸次果复何如。今会融畅。尽是未始有者。而讲评之详。则无甚胜前。追䌷其一二乍更端者。拟更往复而姑未暇焉。然向来閒话间。窃覵高明意思较有圆活不拘滞处。岂亦读易新效耶。今行所得。又为飘洒之助。则岂不尤奇。记中描写曲折。未见有差爽处。所要跋语。实知其不可少者。容俟留神也。洪郎记文。点次入细。往往如画。又情兴逸发。跃如毫楮之上。真奇笔也。每恨东人文集。罕见好游记。而今乃得之于后生。亦一快事。窃怪其不读柳文而神情近之也。仆独留无悰。不废诵课。逦及于孟子。随意抽十馀大篇而成诵。江汉秋阳。始知其十分痛快。恨不早从事耳。千万来伻甚促。只此叙谢。统希崇亮。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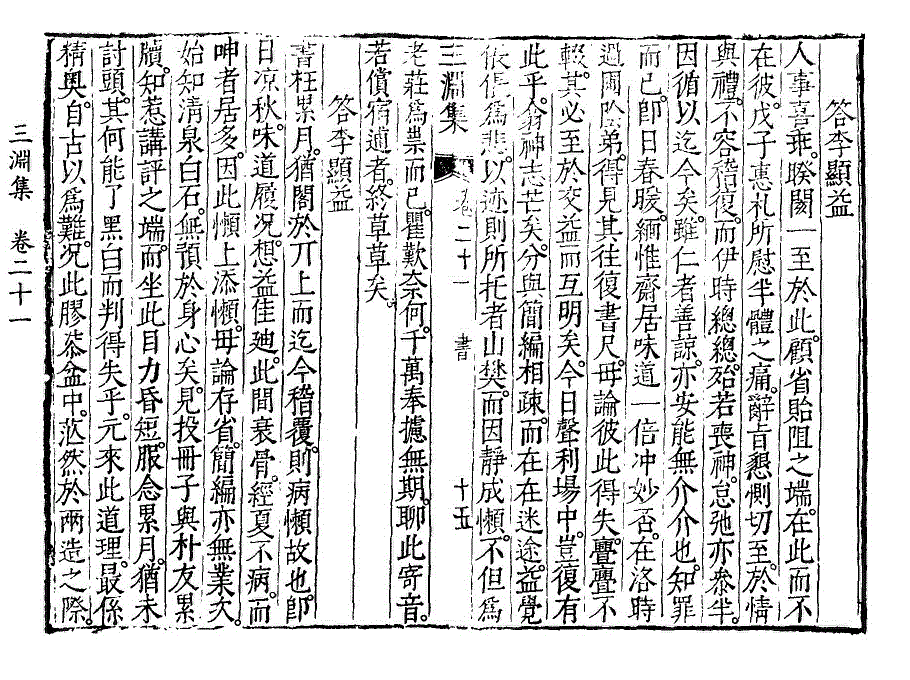 答李显益
答李显益人事喜乖。睽阂一至于此。顾省贻阻之端。在此而不在彼。戊子惠札所慰半体之痛。辞旨恳恻切至。于情与礼。不容稽复。而伊时总总。殆若丧神。怠弛亦参半。因循以迄今矣。虽仁者善谅。亦安能无介介也。知罪而已。即日春暖。缅惟斋居味道一倍冲妙否。在洛时过圃阴弟。得见其往复书尺。毋论彼此得失。亹亹不辍。其必至于交益而互明矣。今日声利场中。岂复有此乎。翕神志芒矣。分与简编相疏。而在在迷途。益觉伥伥为悲。以迹则所托者山樊。而因静成懒。不但为老庄为祟而已。瞿叹奈何。千万奉摅无期。聊此寄音。若偿宿逋者。终草草矣。
答李显益
书枉累月。犹阁于丌上而迄今稽覆。则病懒故也。即日凉秋。味道履况。想益佳迪。此间衰骨。经夏不病。而呻者居多。因此懒上添懒。毋论存省。简编亦无业次。始知清泉白石。无预于身心矣。见投册子与朴友累牍。知惹讲评之端。而坐此目力昏短。服念累月。犹未讨头。其何能了黑白而判得失乎。元来此道理。最系精奥。自古以为难。况此胶漆盆中。茫然于两造之际。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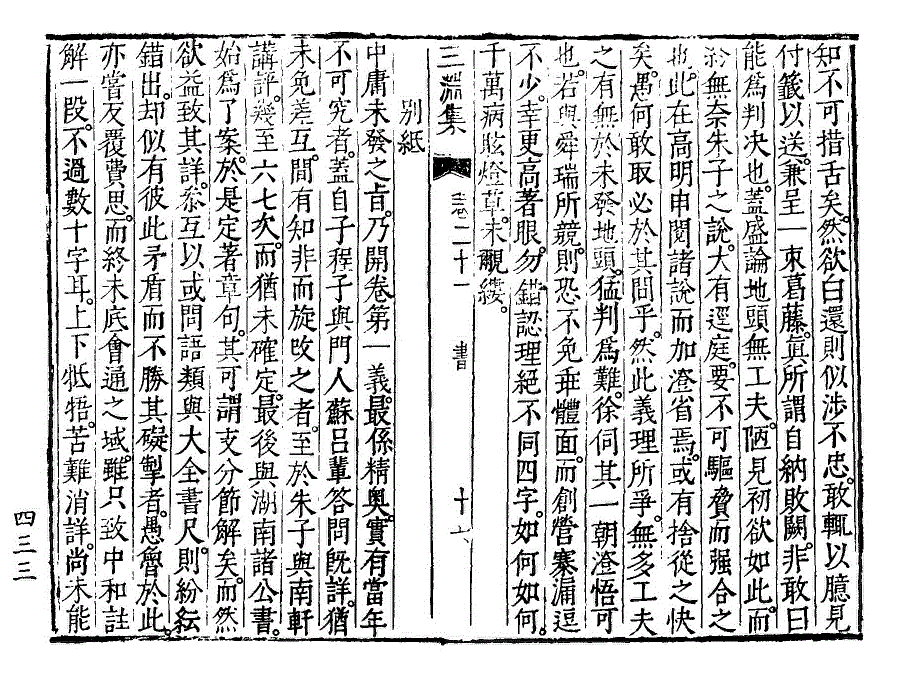 知不可措舌矣。然欲白还则似涉不忠。敢辄以臆见付签以送。兼呈一束葛藤。真所谓自纳败阙。非敢曰能为判决也。盖盛论地头无工夫。陋见初欲如此。而终无奈朱子之说。大有径庭。要不可驱䝱而强合之也。此在高明申阅诸说而加澄省焉。或有舍从之快矣。愚何敢取必于其间乎。然此义理所争。无多工夫之有无于未发地头。猛判为难。徐伺其一朝澄悟可也。若与舜瑞所竞。则恐不免乖体面。而创营寨漏逗不少。幸更高著眼。勿错认理绝不同四字。如何如何。千万病眩灯草。未覼缕。
知不可措舌矣。然欲白还则似涉不忠。敢辄以臆见付签以送。兼呈一束葛藤。真所谓自纳败阙。非敢曰能为判决也。盖盛论地头无工夫。陋见初欲如此。而终无奈朱子之说。大有径庭。要不可驱䝱而强合之也。此在高明申阅诸说而加澄省焉。或有舍从之快矣。愚何敢取必于其间乎。然此义理所争。无多工夫之有无于未发地头。猛判为难。徐伺其一朝澄悟可也。若与舜瑞所竞。则恐不免乖体面。而创营寨漏逗不少。幸更高著眼。勿错认理绝不同四字。如何如何。千万病眩灯草。未覼缕。别纸
中庸未发之旨。乃开卷第一义。最系精奥。实有当年不可究者。盖自子程子与门人苏吕辈答问既详。犹未免差互。间有知非而旋改之者。至于朱子与南轩讲评。几至六七次。而犹未确定。最后与湖南诸公书。始为了案。于是定著章句。其可谓支分节解矣。而然欲益致其详。参互以或问语类与大全书尺。则纷纭错出。却似有彼此矛盾而不胜其碍掣者。愚鲁于此。亦尝反覆费思。而终未底会通之域。虽只致中和注解一段。不过数十字耳。上下牴牾。苦难消详。尚未能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4H 页
 打破柒桶。窃自掩卷而兴喟以为天下之义理。莫斯之难推者矣。今见李朴两贤所与诤卞者。则各持一说。略不相下。确乎自信之笃。未知果孰契子思本旨。而然于朱子诸说。似未曾一一和会而径出于偏主强说者有之。然尚甫之说。大抵仍袭旧说。若曰冲漠中照管不观之观。保其常存之体。依例说去。非所谓杜撰也。若仲谦则曰。未发乃地头。地头无工夫。有工夫。斯为已发。其为说巍巍卓卓。孤迥无倚。不惟煞高于尚甫。殆欲突过朱子。朱子之论未发则实为已卑。乃曰耳目则有闻见矣。手足则有运用矣。以至紸纩蔽前。而可知有赞引矣。甚且援引程子非禅定。而讥许渤禅定为非。则冥寂不可过也。许渤可讥。则窗外之声。可卞谁也。如是说来。所谓未发。亦非悬绝之地。不容著工者也。以视仲谦所云云。果孰为高低哉。且仲谦所谓本体。果悬乎天上而不属人分乎。夫性统乎心。心自有事。语类曰。未发谓之中。发则谓之和。心是做工夫处。以此观之。则心之做工夫。果何间于发未发乎。今以本体寄之人事之外。而谓非工夫所存。是看地头太高而认工夫太重也。以愚见论之。未发工夫。岂真有不可形言者乎。始则收放藏密。中则当
打破柒桶。窃自掩卷而兴喟以为天下之义理。莫斯之难推者矣。今见李朴两贤所与诤卞者。则各持一说。略不相下。确乎自信之笃。未知果孰契子思本旨。而然于朱子诸说。似未曾一一和会而径出于偏主强说者有之。然尚甫之说。大抵仍袭旧说。若曰冲漠中照管不观之观。保其常存之体。依例说去。非所谓杜撰也。若仲谦则曰。未发乃地头。地头无工夫。有工夫。斯为已发。其为说巍巍卓卓。孤迥无倚。不惟煞高于尚甫。殆欲突过朱子。朱子之论未发则实为已卑。乃曰耳目则有闻见矣。手足则有运用矣。以至紸纩蔽前。而可知有赞引矣。甚且援引程子非禅定。而讥许渤禅定为非。则冥寂不可过也。许渤可讥。则窗外之声。可卞谁也。如是说来。所谓未发。亦非悬绝之地。不容著工者也。以视仲谦所云云。果孰为高低哉。且仲谦所谓本体。果悬乎天上而不属人分乎。夫性统乎心。心自有事。语类曰。未发谓之中。发则谓之和。心是做工夫处。以此观之。则心之做工夫。果何间于发未发乎。今以本体寄之人事之外。而谓非工夫所存。是看地头太高而认工夫太重也。以愚见论之。未发工夫。岂真有不可形言者乎。始则收放藏密。中则当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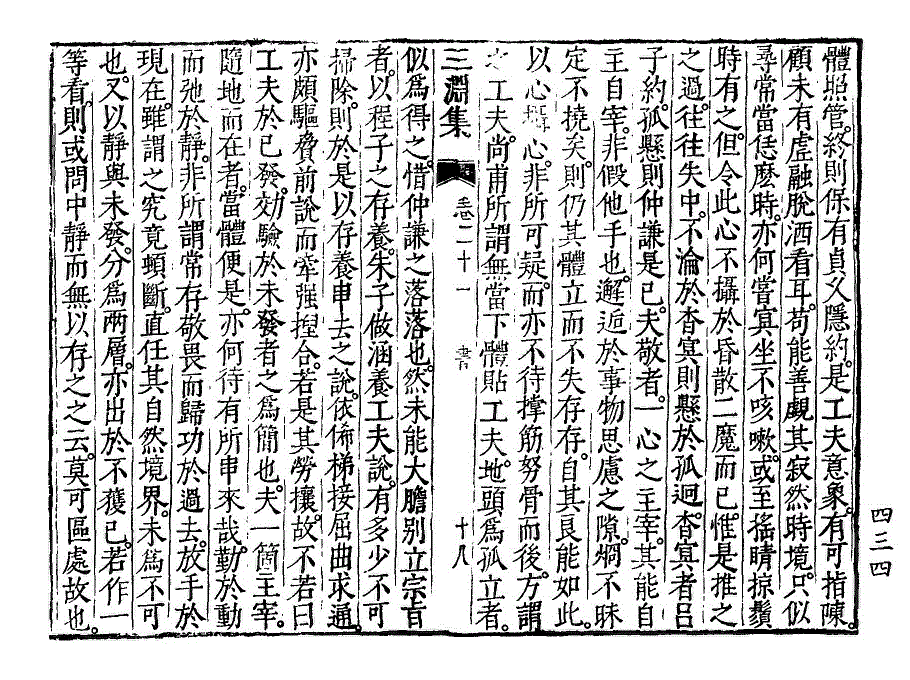 体照管。终则保有贞久隐约。是工夫意象。有可指陈。顾未有虚融脱洒看耳。苟能善觑其寂然时境。只似寻常当恁么时。亦何尝冥坐不咳嗽。或至摇睛掠须时有之。但令此心不摄于昏散二魔而已。惟是推之之过。往往失中。不沦于杳冥则悬于孤迥。杳冥者吕子约。孤悬则仲谦是已。夫敬者。一心之主宰。其能自主自宰。非假他手也。邂逅于事物思虑之隙。烱不昧定不挠矣。则仍其体立而不失存存。自其良能如此。以心摄心。非所可疑。而亦不待撑筋努骨而后。方谓之工夫。尚甫所谓无当下体贴工夫。地头为孤立者。似为得之。惜仲谦之落落也。然未能大胆别立宗旨者。以程子之存养。朱子做涵养工夫说。有多少不可扫除。则于是以存养串去之说。依俙梯接屈曲求通。亦颇驱䝱前说而牵强捏合。若是其劳攘。故不若曰工夫于已发。效验于未发者之为简也。夫一个主宰。随地而在者。当体便是。亦何待有所串来哉。勤于动而弛于静。非所谓常存敬畏而归功于过去。放手于现在。虽谓之究竟顿断。直任其自然境界。未为不可也。又以静与未发。分为两层。亦出于不获已。若作一等看。则或问中静而无以存之之云。莫可区处故也。
体照管。终则保有贞久隐约。是工夫意象。有可指陈。顾未有虚融脱洒看耳。苟能善觑其寂然时境。只似寻常当恁么时。亦何尝冥坐不咳嗽。或至摇睛掠须时有之。但令此心不摄于昏散二魔而已。惟是推之之过。往往失中。不沦于杳冥则悬于孤迥。杳冥者吕子约。孤悬则仲谦是已。夫敬者。一心之主宰。其能自主自宰。非假他手也。邂逅于事物思虑之隙。烱不昧定不挠矣。则仍其体立而不失存存。自其良能如此。以心摄心。非所可疑。而亦不待撑筋努骨而后。方谓之工夫。尚甫所谓无当下体贴工夫。地头为孤立者。似为得之。惜仲谦之落落也。然未能大胆别立宗旨者。以程子之存养。朱子做涵养工夫说。有多少不可扫除。则于是以存养串去之说。依俙梯接屈曲求通。亦颇驱䝱前说而牵强捏合。若是其劳攘。故不若曰工夫于已发。效验于未发者之为简也。夫一个主宰。随地而在者。当体便是。亦何待有所串来哉。勤于动而弛于静。非所谓常存敬畏而归功于过去。放手于现在。虽谓之究竟顿断。直任其自然境界。未为不可也。又以静与未发。分为两层。亦出于不获已。若作一等看。则或问中静而无以存之之云。莫可区处故也。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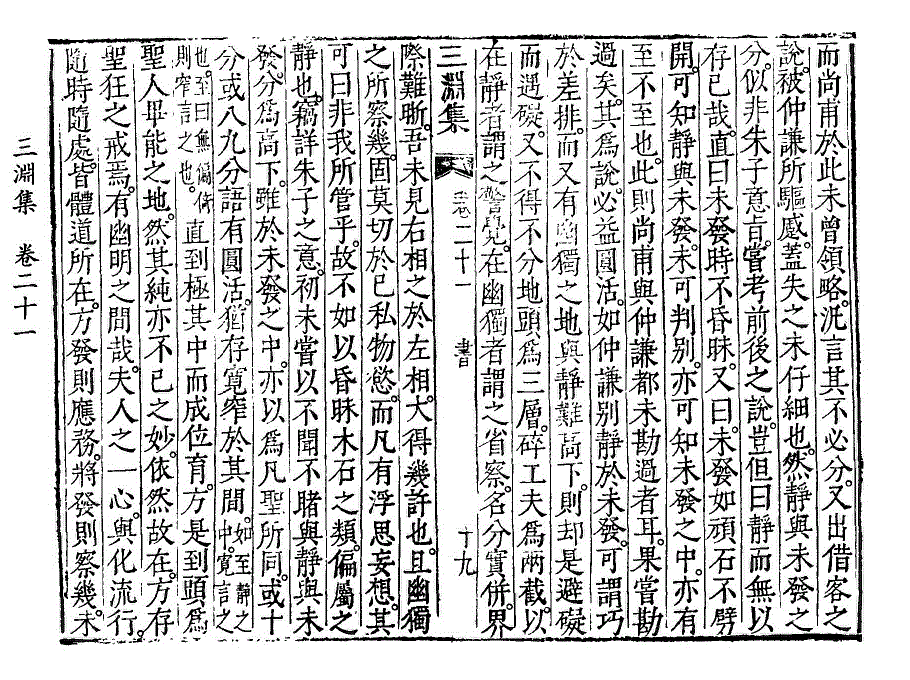 而尚甫于此未曾领略。汎言其不必分。又出借客之说。被仲谦所驱蹙。盖失之未仔细也。然静与未发之分。似非朱子意旨。尝考前后之说。岂但曰静而无以存已哉。直曰未发时不昏昧。又曰。未发如顽石不劈开。可知静与未发。未可判别。亦可知未发之中。亦有至不至也。此则尚甫与仲谦都未勘过者耳。果尝勘过矣。其为说。必益圆活。如仲谦别静于未发。可谓巧于差排。而又有幽独之地与静难高下。则却是避碍而遇碍。又不得不分地头为三层。碎工夫为两截。以在静者谓之警觉。在幽独者谓之省察。名分实并。界际难晢。吾未见右相之于左相。大得几许也。且幽独之所察几。固莫切于己私物欲。而凡有浮思妄想。其可曰非我所管乎。故不如以昏昧木石之类。偏属之静也。窃详朱子之意。初未尝以不闻不睹与静与未发。分为高下。虽于未发之中。亦以为凡圣所同。或十分或八九分语有圆活。犹存宽窄于其间。(如至静之中。宽言之也。至曰无偏倚则窄言之也。)直到极其中而成位育。方是到头为圣人毕能之地。然其纯亦不已之妙。依然故在。方存圣狂之戒焉。有幽明之间哉。夫人之一心。与化流行。随时随处。皆体道所在。方发则应务。将发则察几。未
而尚甫于此未曾领略。汎言其不必分。又出借客之说。被仲谦所驱蹙。盖失之未仔细也。然静与未发之分。似非朱子意旨。尝考前后之说。岂但曰静而无以存已哉。直曰未发时不昏昧。又曰。未发如顽石不劈开。可知静与未发。未可判别。亦可知未发之中。亦有至不至也。此则尚甫与仲谦都未勘过者耳。果尝勘过矣。其为说。必益圆活。如仲谦别静于未发。可谓巧于差排。而又有幽独之地与静难高下。则却是避碍而遇碍。又不得不分地头为三层。碎工夫为两截。以在静者谓之警觉。在幽独者谓之省察。名分实并。界际难晢。吾未见右相之于左相。大得几许也。且幽独之所察几。固莫切于己私物欲。而凡有浮思妄想。其可曰非我所管乎。故不如以昏昧木石之类。偏属之静也。窃详朱子之意。初未尝以不闻不睹与静与未发。分为高下。虽于未发之中。亦以为凡圣所同。或十分或八九分语有圆活。犹存宽窄于其间。(如至静之中。宽言之也。至曰无偏倚则窄言之也。)直到极其中而成位育。方是到头为圣人毕能之地。然其纯亦不已之妙。依然故在。方存圣狂之戒焉。有幽明之间哉。夫人之一心。与化流行。随时随处。皆体道所在。方发则应务。将发则察几。未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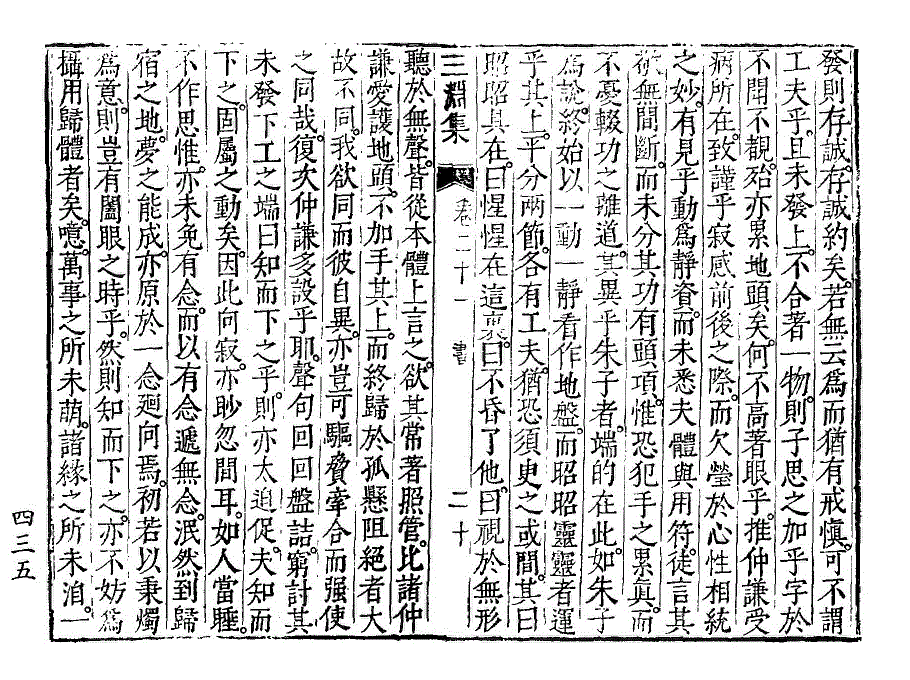 发则存诚。存诚约矣。若无云为而犹有戒慎。可不谓工夫乎。且未发上。不合著一物。则子思之加乎字于不闻不睹。殆亦累地头矣。何不高著眼乎。推仲谦受病所在。致谨乎寂感前后之际。而欠莹于心性相统之妙。有见乎动为静资。而未悉夫体与用符。徒言其敬无间断。而未分其功有头项。惟恐犯手之累真。而不忧辍功之离道。其异乎朱子者。端的在此。如朱子为说。终始以一动一静看作地盘。而昭昭灵灵者运乎其上。平分两节。各有工夫。犹恐须臾之或间。其曰昭昭具在。曰惺惺在这里。曰不昏了他。曰视于无形听于无声。皆从本体上言之。欲其常著照管。比诸仲谦爱护地头。不加手其上。而终归于孤悬阻绝者大故不同。我欲同而彼自异。亦岂可驱䝱牵合而强使之同哉。复次仲谦多设乎耶。声句回回盘诘。穷讨其未发下工之端曰知而下之乎。则亦太迫促。夫知而下之。固属之动矣。因此向寂。亦眇忽间耳。如人当睡。不作思惟。亦未免有念。而以有念递无念。泯然到归宿之地。梦之能成。亦原于一念回向焉。初若以秉烛为意。则岂有阖眼之时乎。然则知而下之。亦不妨为摄用归体者矣。噫。万事之所未萌。诸缘之所未洎。一
发则存诚。存诚约矣。若无云为而犹有戒慎。可不谓工夫乎。且未发上。不合著一物。则子思之加乎字于不闻不睹。殆亦累地头矣。何不高著眼乎。推仲谦受病所在。致谨乎寂感前后之际。而欠莹于心性相统之妙。有见乎动为静资。而未悉夫体与用符。徒言其敬无间断。而未分其功有头项。惟恐犯手之累真。而不忧辍功之离道。其异乎朱子者。端的在此。如朱子为说。终始以一动一静看作地盘。而昭昭灵灵者运乎其上。平分两节。各有工夫。犹恐须臾之或间。其曰昭昭具在。曰惺惺在这里。曰不昏了他。曰视于无形听于无声。皆从本体上言之。欲其常著照管。比诸仲谦爱护地头。不加手其上。而终归于孤悬阻绝者大故不同。我欲同而彼自异。亦岂可驱䝱牵合而强使之同哉。复次仲谦多设乎耶。声句回回盘诘。穷讨其未发下工之端曰知而下之乎。则亦太迫促。夫知而下之。固属之动矣。因此向寂。亦眇忽间耳。如人当睡。不作思惟。亦未免有念。而以有念递无念。泯然到归宿之地。梦之能成。亦原于一念回向焉。初若以秉烛为意。则岂有阖眼之时乎。然则知而下之。亦不妨为摄用归体者矣。噫。万事之所未萌。诸缘之所未洎。一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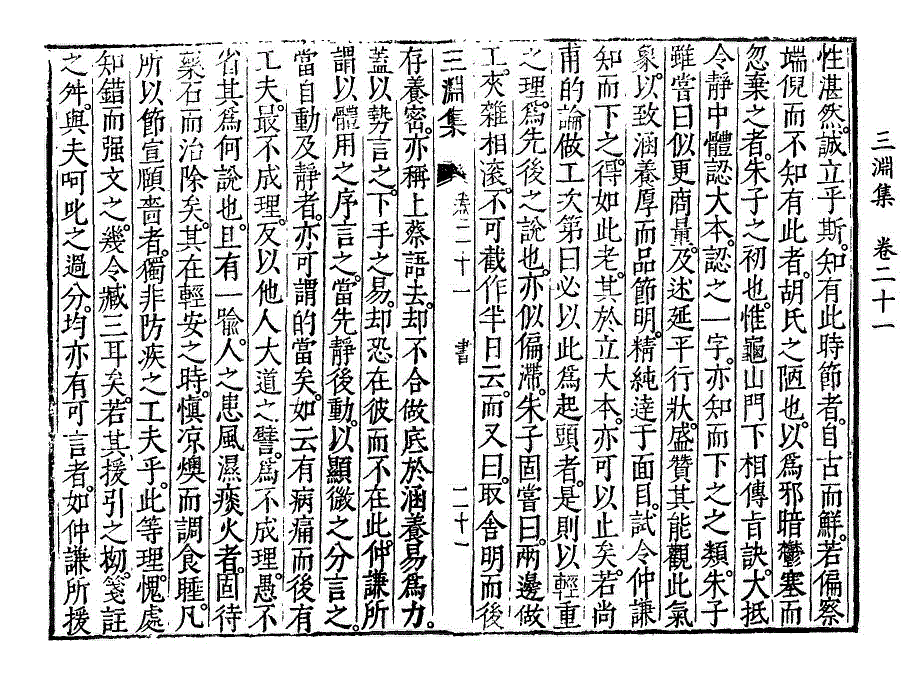 性湛然。诚立乎斯。知有此时节者。自古而鲜。若偏察端倪而不知有此者。胡氏之陋也。以为邪暗郁塞而忽弃之者。朱子之初也。惟龟山门下相传旨诀。大抵令静中体认大本。认之一字。亦知而下之之类。朱子虽尝曰似更商量。及述延平行状。盛赞其能观此气象。以致涵养厚而品节明。精纯达于面目。试令仲谦知而下之。得如此老。其于立大本。亦可以止矣。若尚甫的论做工次第曰必以此为起头者。是则以轻重之理。为先后之说也。亦似偏滞。朱子固尝曰。两边做工。夹杂相滚。不可截作半日云。而又曰。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亦称上蔡语去。却不合做底于涵养易为力。盖以势言之。下手之易。却恐在彼而不在此。仲谦所谓以体用之序言之。当先静后动。以显微之分言之。当自动及静者。亦可谓的当矣。如云有病痛而后有工夫。最不成理。反以他人大道之譬。为不成理。愚不省其为何说也。且有一喻。人之患风湿痰火者。固待药石而治除矣。其在轻安之时。慎凉燠而调食睡。凡所以节宣颐啬者。独非防疾之工夫乎。此等理。愧处知错而强文之。几令臧三耳矣。若其援引之拗。笺注之舛。与夫呵叱之过分。均亦有可言者。如仲谦所援
性湛然。诚立乎斯。知有此时节者。自古而鲜。若偏察端倪而不知有此者。胡氏之陋也。以为邪暗郁塞而忽弃之者。朱子之初也。惟龟山门下相传旨诀。大抵令静中体认大本。认之一字。亦知而下之之类。朱子虽尝曰似更商量。及述延平行状。盛赞其能观此气象。以致涵养厚而品节明。精纯达于面目。试令仲谦知而下之。得如此老。其于立大本。亦可以止矣。若尚甫的论做工次第曰必以此为起头者。是则以轻重之理。为先后之说也。亦似偏滞。朱子固尝曰。两边做工。夹杂相滚。不可截作半日云。而又曰。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亦称上蔡语去。却不合做底于涵养易为力。盖以势言之。下手之易。却恐在彼而不在此。仲谦所谓以体用之序言之。当先静后动。以显微之分言之。当自动及静者。亦可谓的当矣。如云有病痛而后有工夫。最不成理。反以他人大道之譬。为不成理。愚不省其为何说也。且有一喻。人之患风湿痰火者。固待药石而治除矣。其在轻安之时。慎凉燠而调食睡。凡所以节宣颐啬者。独非防疾之工夫乎。此等理。愧处知错而强文之。几令臧三耳矣。若其援引之拗。笺注之舛。与夫呵叱之过分。均亦有可言者。如仲谦所援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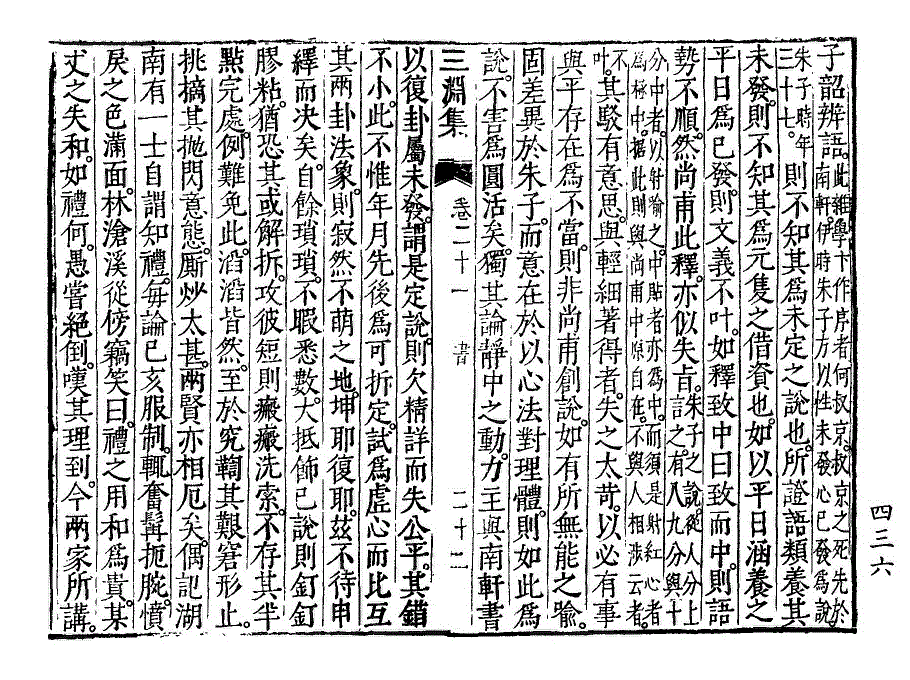 子韶辨语。(此杂学卞作序者何叔京。叔京之死先于南轩。伊时朱子方以性未发心已发为说。朱子时年三十七。)则不知其为未定之说也。所證语类养其未发。则不知其为元只之借资也。如以平日涵养之平日为已发。则文义不叶。如释致中曰致而中。则语势不顺。然尚甫此释。亦似失旨。(朱子之说。从人分上言之。有八九分与十分中者。以射喻之。中贴者亦为中。而须是射红心者为极中。据此则与尚甫中原自在。不与人相涉云者。不叶。)其驳有意思。与轻细著得者。失之太苛。以必有事与平存在为不当。则非尚甫创说。如有所无能之喻。固差异于朱子。而意在于以心法对理体。则如此为说。不害为圆活矣。独其论静中之动。力主与南轩书以复卦属未发。谓是定说。则欠精详而失公平。其错不小。此不惟年月先后为可折定。试为虚心而比互其两卦法象。则寂然不萌之地。坤耶复耶。玆不待申绎而决矣。自馀琐琐。不暇悉数。大抵饰已说则钉钉胶粘。犹恐其或解拆。攻彼短则瘢瘢洗索。不存其半点完处。例难免此。滔滔皆然。至于究鞫其艰窘形止。挑摘其抛闪意态。厮炒太甚。两贤亦相厄矣。偶记湖南有一士自谓知礼。每论己亥服制。辄奋髯扼腕。愤戾之色满面。林沧溪从傍窃笑曰。礼之用和为贵。某丈之失和。如礼何。愚尝绝倒。叹其理到。今两家所讲。
子韶辨语。(此杂学卞作序者何叔京。叔京之死先于南轩。伊时朱子方以性未发心已发为说。朱子时年三十七。)则不知其为未定之说也。所證语类养其未发。则不知其为元只之借资也。如以平日涵养之平日为已发。则文义不叶。如释致中曰致而中。则语势不顺。然尚甫此释。亦似失旨。(朱子之说。从人分上言之。有八九分与十分中者。以射喻之。中贴者亦为中。而须是射红心者为极中。据此则与尚甫中原自在。不与人相涉云者。不叶。)其驳有意思。与轻细著得者。失之太苛。以必有事与平存在为不当。则非尚甫创说。如有所无能之喻。固差异于朱子。而意在于以心法对理体。则如此为说。不害为圆活矣。独其论静中之动。力主与南轩书以复卦属未发。谓是定说。则欠精详而失公平。其错不小。此不惟年月先后为可折定。试为虚心而比互其两卦法象。则寂然不萌之地。坤耶复耶。玆不待申绎而决矣。自馀琐琐。不暇悉数。大抵饰已说则钉钉胶粘。犹恐其或解拆。攻彼短则瘢瘢洗索。不存其半点完处。例难免此。滔滔皆然。至于究鞫其艰窘形止。挑摘其抛闪意态。厮炒太甚。两贤亦相厄矣。偶记湖南有一士自谓知礼。每论己亥服制。辄奋髯扼腕。愤戾之色满面。林沧溪从傍窃笑曰。礼之用和为贵。某丈之失和。如礼何。愚尝绝倒。叹其理到。今两家所讲。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7H 页
 亦岂非不偏不倚。若鉴空衡平者乎。从初商量之意。非欲取胜笔舌。盖将审其偏而归乎中。著实受用之为贵。及夫说来说去中忘此意。不自觉人我山高。壁垒金固。务在一胜。不暇问壮老曲直。到这里。殆似无些子鉴意思。无些子衡意思。岂所谓争时急。不知出此者耶。夫莫悦乎朋友讲习。而不善为之。或无益而有损。宁可不反思其故耶。惟此义理。实为大头脑。不容二三其说。如欲熟讲而归一。则广设函三之席。集四方贤俊以讨之。先须戒心。以颜子为法。不见其有馀不足之所在。然后大开眼看觑。大开口讲评。庶有融契。与享丽泽之乐矣。不亦快哉。不然而人各偏见。主先入而争閒气。终亦无益也已矣。抑两贤识解名言之妙。剖纤透微。殆欲见虱乎车轮。斯可畏已。独恐于上面无形影。心目或不到。则苦相辨诘。易损其真。且暂忘言。徐伺其涵养积而澄悟到。为未晚也。如何如何。既非堂上之人。强为是判。亦太僭越。敢复以退溪告高峰者为两贤诵之曰。其心求胜而不揆诸道者。终无可合之理。志在明道而两无私意者。必有同归之日。凡百讲道之士。其亦退步而存省也哉。
亦岂非不偏不倚。若鉴空衡平者乎。从初商量之意。非欲取胜笔舌。盖将审其偏而归乎中。著实受用之为贵。及夫说来说去中忘此意。不自觉人我山高。壁垒金固。务在一胜。不暇问壮老曲直。到这里。殆似无些子鉴意思。无些子衡意思。岂所谓争时急。不知出此者耶。夫莫悦乎朋友讲习。而不善为之。或无益而有损。宁可不反思其故耶。惟此义理。实为大头脑。不容二三其说。如欲熟讲而归一。则广设函三之席。集四方贤俊以讨之。先须戒心。以颜子为法。不见其有馀不足之所在。然后大开眼看觑。大开口讲评。庶有融契。与享丽泽之乐矣。不亦快哉。不然而人各偏见。主先入而争閒气。终亦无益也已矣。抑两贤识解名言之妙。剖纤透微。殆欲见虱乎车轮。斯可畏已。独恐于上面无形影。心目或不到。则苦相辨诘。易损其真。且暂忘言。徐伺其涵养积而澄悟到。为未晚也。如何如何。既非堂上之人。强为是判。亦太僭越。敢复以退溪告高峰者为两贤诵之曰。其心求胜而不揆诸道者。终无可合之理。志在明道而两无私意者。必有同归之日。凡百讲道之士。其亦退步而存省也哉。签论(此即李显益与朴弼周往复者。而先生就加签谕焉。)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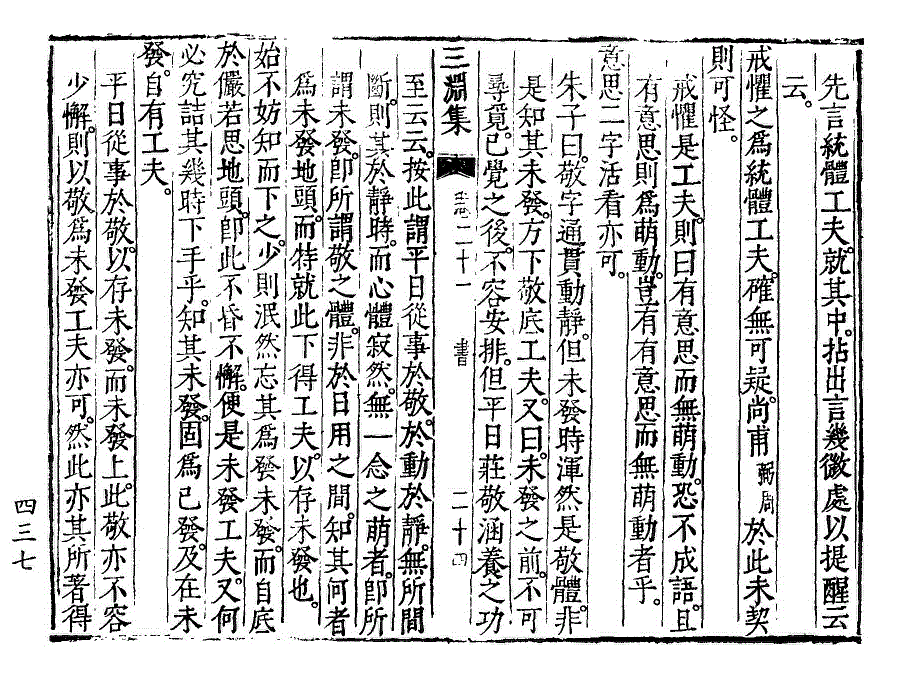 先言统体工夫。就其中。拈出言几微处以提醒云云。
先言统体工夫。就其中。拈出言几微处以提醒云云。戒惧之为统体工夫。确无可疑。尚甫(弼周)于此未契则可怪。
戒惧是工夫。则曰有意思而无萌动。恐不成语。且有意思则为萌动。岂有有意思而无萌动者乎。
意思二字活看亦可。
朱子曰。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浑然是敬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又曰。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云云。按此谓平日从事于敬。于动于静。无所间断。则其于静时。而心体寂然。无一念之萌者。即所谓未发。即所谓敬之体。非于日用之间。知其何者为未发地头。而特就此下得工夫。以存未发也。
始不妨知而下之。少则泯然忘其为发未发。而自底于俨若思地头。即此不昏不懈。便是未发工夫。又何必究诘其几时下手乎。知其未发。固为已发。及在未发。自有工夫。
平日从事于敬。以存未发。而未发上。此敬亦不容少懈。则以敬为未发工夫亦可。然此亦其所著得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8H 页
 者在平日。而非于未发地头。始著得者。则以此为未发工夫不可。
者在平日。而非于未发地头。始著得者。则以此为未发工夫不可。既以敬不懈为未发工夫。而又欲归功于平日。无乃矛盾乎。
张子韶中庸解曰。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朱子辨曰。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按此说。非谓未发上。无戒慎恐惧也。盖谓戒慎恐惧。贯彻动静。而其在静时者为未发。非于未发地头。特下戒慎恐惧故耳。
决是未定之说。如是强解不得。
朱子以收拾存在。为戒惧工夫。故人多以此为未发工夫。然此亦谓之戒惧工夫则可。谓之未发工夫则不可云云。
以平平略略。为未发工夫。未为不可。或问未动前戒惧。朱子答以略略收拾在这里。岂未经眼耶。
静有兼身之未与物接及心之一念未萌者言。虽未能一念未萌。而只是未与物接者。亦可谓之静。未发则必并一念未萌。然后为未发耳。静较未发地界阔。未发为静里面事。静未必皆未发。而未发则静。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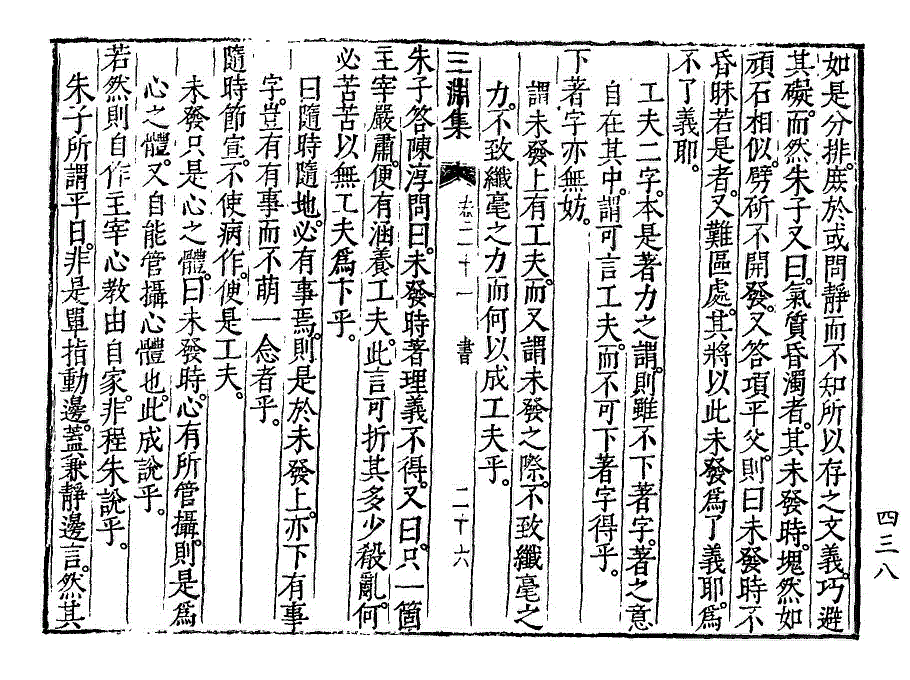 如是分排。庶于或问静而不知所以存之文义。巧避其碍。而然朱子又曰。气质昏浊者。其未发时。块然如顽石相似。劈斫不开发。又答项平父。则曰未发时不昏昧若是者。又难区处。其将以此未发为了义耶。为不了义耶。
如是分排。庶于或问静而不知所以存之文义。巧避其碍。而然朱子又曰。气质昏浊者。其未发时。块然如顽石相似。劈斫不开发。又答项平父。则曰未发时不昏昧若是者。又难区处。其将以此未发为了义耶。为不了义耶。工夫二字。本是著力之谓。则虽不下著字。著之意自在其中。谓可言工夫。而不可下著字得乎。
下著字亦无妨。
谓未发上有工夫。而又谓未发之际。不致纤毫之力。不致纤毫之力而何以成工夫乎。
朱子答陈淳问曰。未发时著理义不得。又曰。只一个主宰严肃。便有涵养工夫。此言可折其多少殽乱。何必苦苦以无工夫为卞乎。
曰随时随地。必有事焉。则是于未发上。亦下有事字。岂有有事而不萌一念者乎。
随时节宣。不使病作。便是工夫。
未发只是心之体。曰未发时。心有所管摄。则是为心之体。又自能管摄心体也。此成说乎。
若然则自作主宰心教由自家。非程朱说乎。
朱子所谓平日。非是单指动边。盖兼静边言。然其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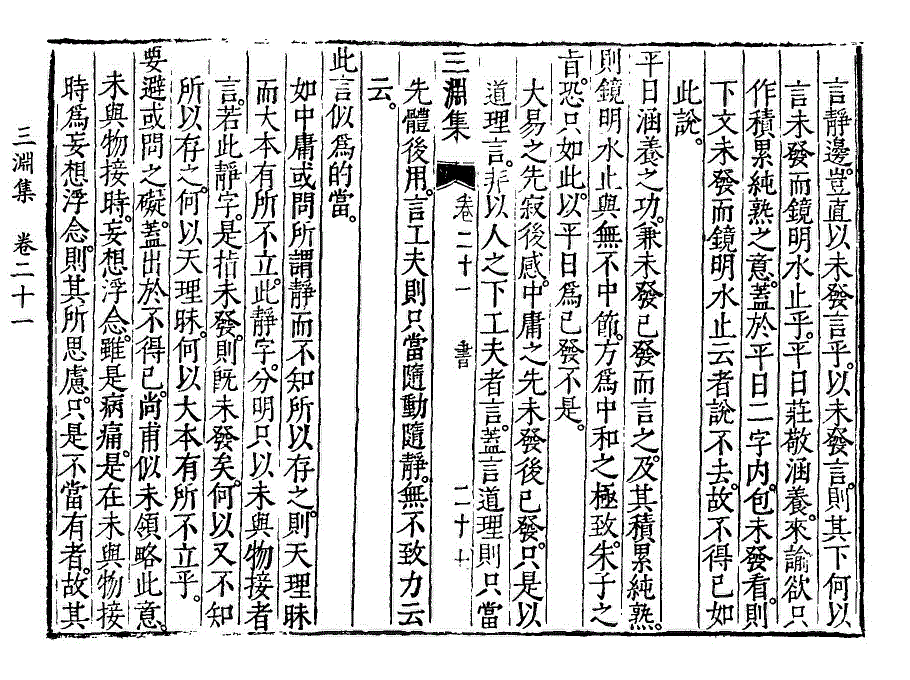 言静边。岂直以未发言乎。以未发言。则其下何以言未发而镜明水止乎。平日庄敬涵养。来谕欲只作积累纯熟之意。盖于平日二字内。包未发看。则下文未发而镜明水止云者说不去。故不得已如此说。
言静边。岂直以未发言乎。以未发言。则其下何以言未发而镜明水止乎。平日庄敬涵养。来谕欲只作积累纯熟之意。盖于平日二字内。包未发看。则下文未发而镜明水止云者说不去。故不得已如此说。平日涵养之功。兼未发已发而言之。及其积累纯熟。则镜明水止与无不中节。方为中和之极致。朱子之旨。恐只如此。以平日为已发不是。
大易之先寂后感。中庸之先未发后已发。只是以道理言。非以人之下工夫者言。盖言道理则只当先体后用。言工夫则只当随动随静。无不致力云云。
此言似为的当。
如中庸或问所谓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则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静字。分明只以未与物接者言。若此静字。是指未发。则既未发矣。何以又不知所以存之。何以天理昧。何以大本有所不立乎。
要避或问之碍。盖出于不得已。尚甫似未领略此意。
未与物接时。妄想浮念。虽是病痛。是在未与物接时为妄想浮念。则其所思虑。只是不当有者。故其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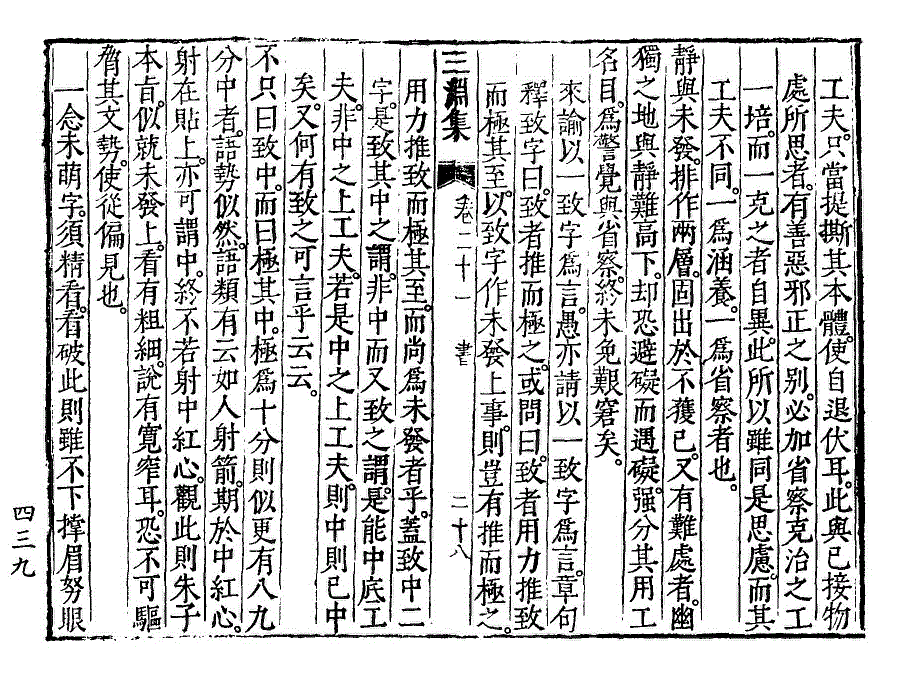 工夫。只当提撕其本体。使自退伏耳。此与已接物处所思者。有善恶邪正之别。必加省察克治之工一培。而一克之者自异。此所以虽同是思虑。而其工夫不同。一为涵养。一为省察者也。
工夫。只当提撕其本体。使自退伏耳。此与已接物处所思者。有善恶邪正之别。必加省察克治之工一培。而一克之者自异。此所以虽同是思虑。而其工夫不同。一为涵养。一为省察者也。静与未发。排作两层。固出于不获已。又有难处者。幽独之地与静难高下。却恐避碍而遇碍。强分其用工名目。为警觉与省察。终未免艰窘矣。
来谕以一致字为言。愚亦请以一致字为言。章句释致字曰。致者推而极之。或问曰。致者用力推致而极其至。以致字作未发上事。则岂有推而极之。用力推致而极其至。而尚为未发者乎。盖致中二字。是致其中之谓。非中而又致之谓。是能中底工夫。非中之上工夫。若是中之上工夫。则中则已中矣。又何有致之可言乎云云。
不只曰致中。而曰极其中。极为十分则似更有八九分中者。语势似然。语类有云如人射箭。期于中红心。射在贴上。亦可谓中。终不若射中红心。观此则朱子本旨。似就未发上。看有粗细。说有宽窄耳。恐不可驱胁其文势。使从偏见也。
一念未萌字。须精看。看破此则虽不下撑眉努眼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0H 页
 等语。只如来教所言轻细著得者。亦说不去。
等语。只如来教所言轻细著得者。亦说不去。其下文又曰。只是耸然提起。又曰防闲其未发。若此云云。虽谓之轻细著得。不为不足矣。
近得朱子一语。有曰戒惧是未发。然只做未发也。不得便是所以养其未发。此更分晓。
引此为證。却恐为元只地。
朱子以必有事焉。为静中之动。则有事字。贴动字说。而朱子此说。与答南轩中和说之初见同。则其非定论明矣云云。
必有事焉。朱子释之以其心俨然。常若有事云尔。则以喻未发工夫。未见其失答南轩书果非定论。
中庸或问不知所以存之云云。来谕以为借客形主云者。是谓朱子虽知未发里面。不可著得不在不明不立等语。而以形容之难。而借此以言之云耳。夫未发是何等精微底物事。而其里面所无者。却借来于外以添之耶。才著动意则非未发。况又著病痛意。则何得为未发耶。朱子之旨。决不如此。
借客之说艰窘。
朱子能知觉所知觉之云。与折柳看花语。若不同而实无不同。愚意能所分别。只可于著工夫处言。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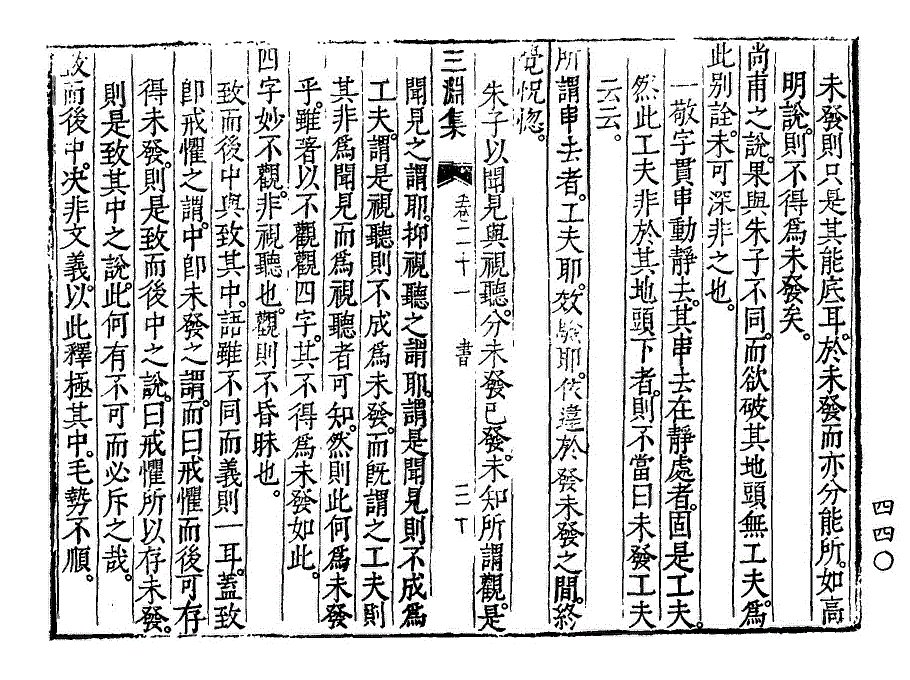 未发则只是其能底耳。于未发而亦分能所。如高明说。则不得为未发矣。
未发则只是其能底耳。于未发而亦分能所。如高明说。则不得为未发矣。尚甫之说。果与朱子不同。而欲破其地头无工夫。为此别诠。未可深非之也。
一敬字贯串动静去。其串去在静处者。固是工夫。然此工夫非于其地头下者。则不当曰未发工夫云云。
所谓串去者。工夫耶。效验耶。依违于发未发之间。终觉恍惚。
朱子以闻见与视听。分未发已发。未知所谓观。是闻见之谓耶。抑视听之谓耶。谓是闻见则不成为工夫。谓是视听则不成为未发。而既谓之工夫则其非为闻见而为视听者可知。然则此何为未发乎。虽著以不观观四字。其不得为未发如此。
四字妙不观。非视听也。观则不昏昧也。
致而后中与致其中。语虽不同而义则一耳。盖致即戒惧之谓。中即未发之谓。而曰戒惧而后可存得未发。则是致而后中之说。曰戒惧所以存未发。则是致其中之说。此何有不可而必斥之哉。
致而后中。决非文义。以此释极其中。毛势不顺。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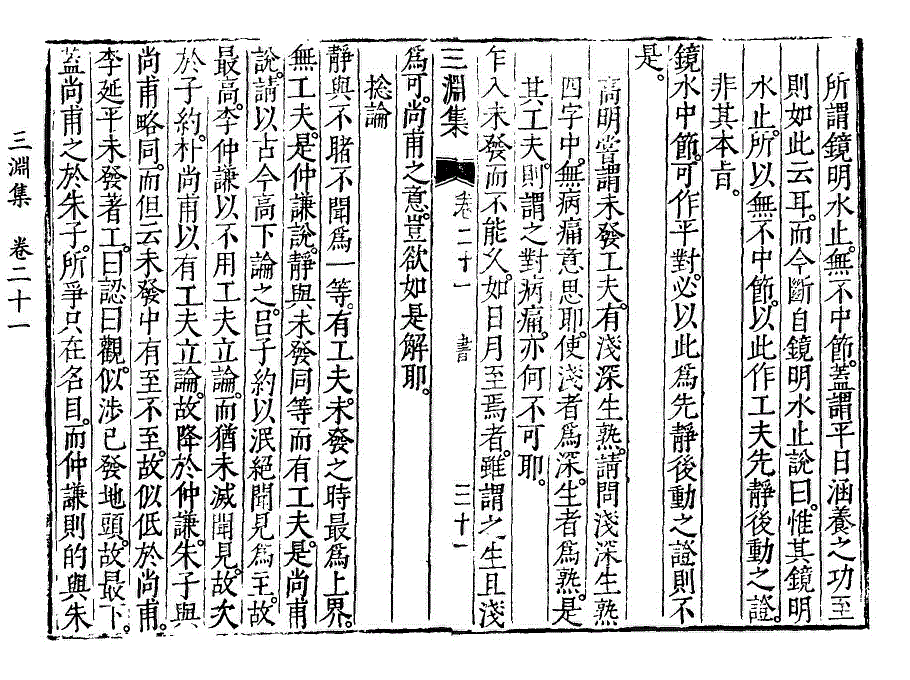 所谓镜明水止。无不中节。盖谓平日涵养之功至则如此云耳。而今断自镜明水止说曰。惟其镜明水止。所以无不中节。以此作工夫先静后动之證。非其本旨。
所谓镜明水止。无不中节。盖谓平日涵养之功至则如此云耳。而今断自镜明水止说曰。惟其镜明水止。所以无不中节。以此作工夫先静后动之證。非其本旨。镜水中节。可作平对。必以此为先静后动之證则不是。
高明尝谓未发工夫。有浅深生熟。请问浅深生熟四字中。无病痛意思耶。使浅者为深。生者为熟。是其工夫。则谓之对病痛。亦何不可耶。
乍入未发而不能久。如日月至焉者。虽谓之生且浅为可。尚甫之意。岂欲如是解耶。
总论
静与不睹不闻为一等。有工夫。未发之时最为上界。无工夫。是仲谦说。静与未发同等而有工夫。是尚甫说。请以古今高下论之。吕子约以泯绝闻见为主。故最高。李仲谦以不用工夫立论。而犹未灭闻见。故次于子约。朴尚甫以有工夫立论。故降于仲谦。朱子与尚甫略同。而但云未发中有至不至。故似低于尚甫。李延平未发著工。曰认曰观。似涉已发地头。故最下。盖尚甫之于朱子。所争只在名目。而仲谦则的与朱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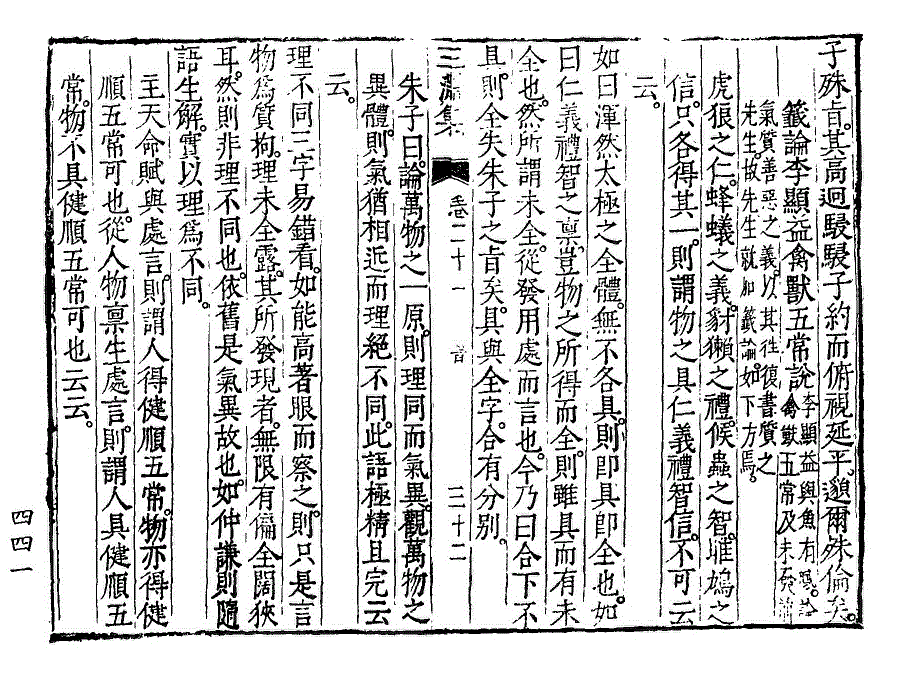 子殊旨。其高迥骎骎子约而俯视延平。邈尔殊伦矣。
子殊旨。其高迥骎骎子约而俯视延平。邈尔殊伦矣。签论李显益禽兽五常说(李显益与鱼有凤。论禽兽五常及未发前气质善恶之义。以其往复书质之先生。故先生就加签论。如下方焉。)
虎狼之仁。蜂蚁之义。豺獭之礼。候虫之智。雎鸠之信。只各得其一。则谓物之具仁义礼智信。不可云云。
如曰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则即具即全也。如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则虽具而有未全也。然所谓未全。从发用处而言也。今乃曰合下不具。则全失朱子之旨矣。具与全字。合有分别。
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语极精且完云云。
理不同三字易错看。如能高著眼而察之。则只是言物为质拘。理未全露。其所发现者。无限有偏全阔狭耳。然则非理不同也。依旧是气异故也。如仲谦则随语生解。实以理为不同。
主天命赋与处言。则谓人得健顺五常。物亦得健顺五常可也。从人物禀生处言。则谓人具健顺五常。物不具健顺五常可也云云。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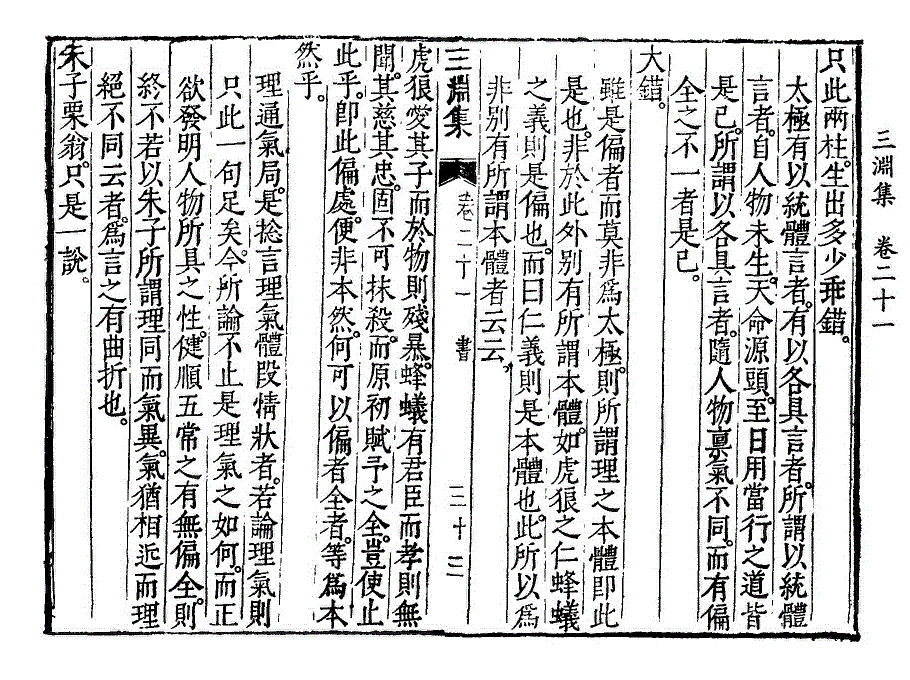 只此两柱。生出多少乖错。
只此两柱。生出多少乖错。太极有以统体言者。有以各具言者。所谓以统体言者。自人物未生。天命源头。至日用当行之道皆是已。所谓以各具言者。随人物禀气不同。而有偏全之不一者是已。
大错。
虽是偏者而莫非为太极。则所谓理之本体即此是也。非于此外别有所谓本体。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则是偏也。而曰仁义则是本体也。此所以为非别有所谓本体者云云。
虎狼爱其子而于物则残暴。蜂蚁有君臣而孝则无闻。其慈其忠。固不可抹杀。而原初赋予之全。岂使止此乎。即此偏处。便非本然。何可以偏者全者。等为本然乎。
理通气局。是总言理气体段情状者。若论理气则只此一句足矣。今所论不止是理气之如何。而正欲发明人物所具之性。健顺五常之有无偏全。则终不若以朱子所谓理同而气异。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云者。为言之有曲折也。
朱子栗翁。只是一说。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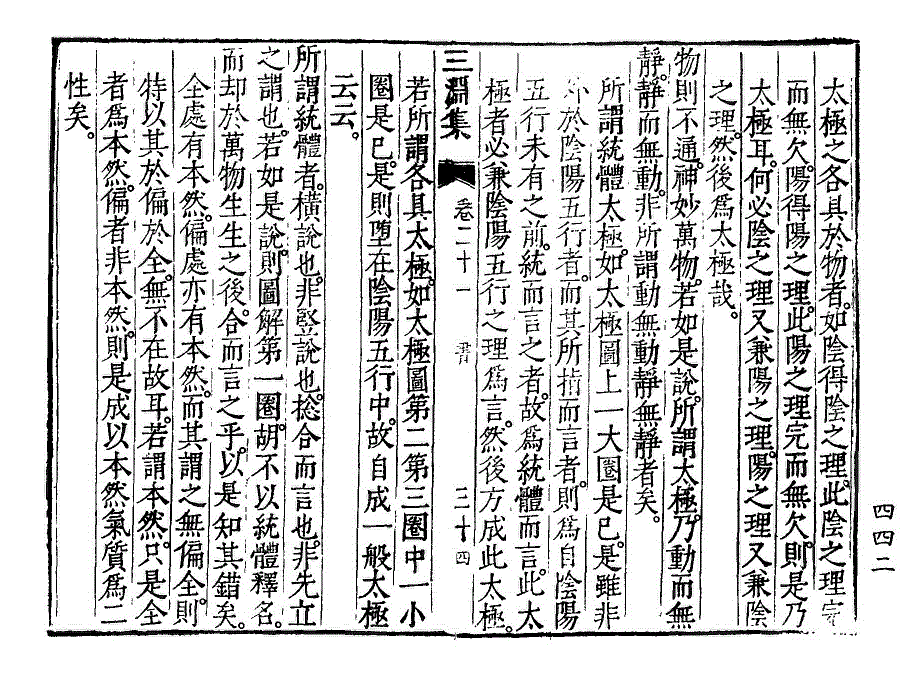 太极之各具于物者。如阴得阴之理。此阴之理完而无欠。阳得阳之理。此阳之理完而无欠。则是乃太极耳。何必阴之理又兼阳之理。阳之理又兼阴之理。然后为太极哉。
太极之各具于物者。如阴得阴之理。此阴之理完而无欠。阳得阳之理。此阳之理完而无欠。则是乃太极耳。何必阴之理又兼阳之理。阳之理又兼阴之理。然后为太极哉。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若如是说。所谓太极。乃动而无静。静而无动。非所谓动无动静无静者矣。
所谓统体太极。如太极图上一大圈是已。是虽非外于阴阳五行者。而其所指而言者。则为自阴阳五行未有之前。统而言之者。故为统体而言。此太极者必兼阴阳五行之理为言。然后方成此太极。若所谓各具太极。如太极图第二第三圈中一小圈是已。是则堕在阴阳五行中。故自成一般太极云云。
所谓统体者。横说也。非竖说也。总合而言也。非先立之谓也。若如是说。则图解第一圈。胡不以统体释名。而却于万物生生之后。合而言之乎。以是知其错矣。
全处有本然。偏处亦有本然。而其谓之无偏全。则特以其于偏于全。无不在故耳。若谓本然。只是全者为本然。偏者非本然。则是成以本然气质为二性矣。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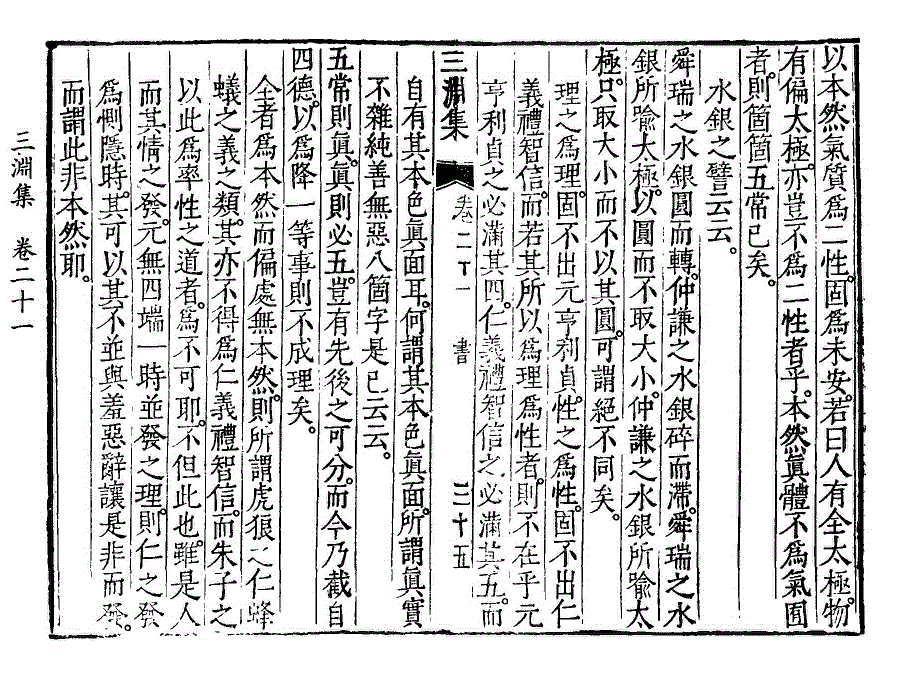 以本然气质为二性。固为未安。若曰人有全太极。物有偏太极。亦岂不为二性者乎。本然真体不为气囿者。则个个五常已矣。
以本然气质为二性。固为未安。若曰人有全太极。物有偏太极。亦岂不为二性者乎。本然真体不为气囿者。则个个五常已矣。水银之譬云云。
舜瑞之水银圆而转。仲谦之水银碎而滞。舜瑞之水银所喻太极。以圆而不取大小。仲谦之水银所喻太极。只取大小而不以其圆。可谓绝不同矣。
理之为理。固不出元亨利贞。性之为性。固不出仁义礼智信。而若其所以为理为性者。则不在乎元亨利贞之必满其四。仁义礼智信之必满其五。而自有其本色真面耳。何谓其本色真面。所谓真实不杂纯善无恶八个字是已云云。
五常则真。真则必五。岂有先后之可分。而今乃截自四德。以为降一等事则不成理矣。
全者为本然而偏处无本然。则所谓虎狼之仁蜂蚁之义之类。其亦不得为仁义礼智信。而朱子之以此为率性之道者。为不可耶。不但此也。虽是人而其情之发。元无四端一时并发之理。则仁之发为恻隐时。其可以其不并与羞恶辞让是非而发。而谓此非本然耶。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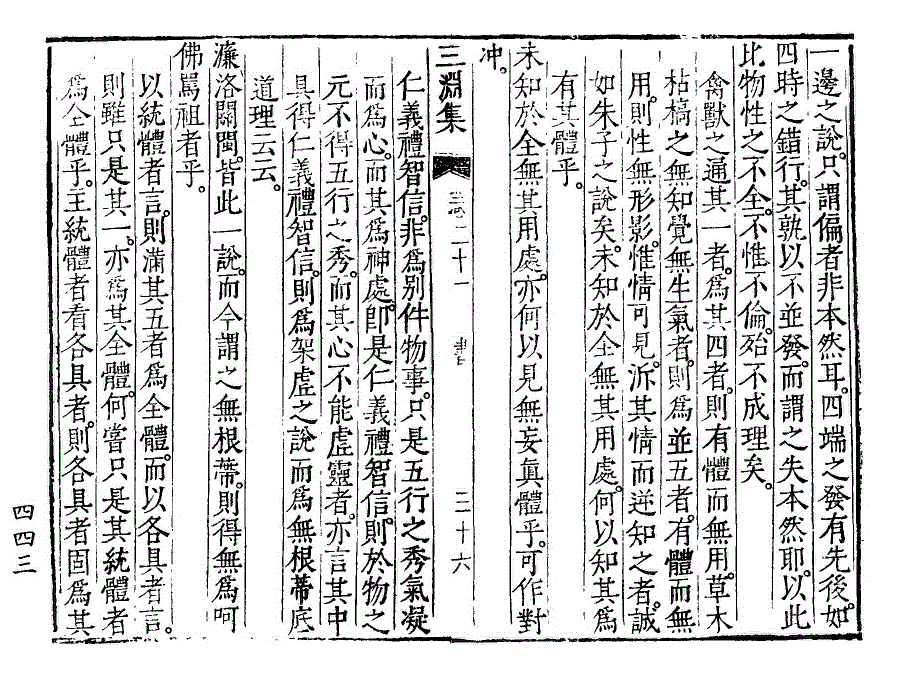 一边之说。只谓偏者非本然耳。四端之发有先后。如四时之错行。其孰以不并发。而谓之失本然耶。以此比物性之不全。不惟不伦。殆不成理矣。
一边之说。只谓偏者非本然耳。四端之发有先后。如四时之错行。其孰以不并发。而谓之失本然耶。以此比物性之不全。不惟不伦。殆不成理矣。禽兽之通其一者。为其四者。则有体而无用。草木枯槁之无知觉无生气者。则为并五者。有体而无用。则性无形影。惟情可见。溯其情而逆知之者。诚如朱子之说矣。未知于全无其用处。何以知其为有其体乎。
未知于全无其用处。亦何以见无妄真体乎。可作对冲。
仁义礼智信。非为别件物事。只是五行之秀气凝而为心。而其为神处。即是仁义礼智信。则于物之元不得五行之秀。而其心不能虚灵者。亦言其中具得仁义礼智信。则为架虚之说而为无根蒂底道理云云。
濂洛关闽。皆此一说。而今谓之无根蒂。则得无为呵佛骂祖者乎。
以统体者言。则满其五者为全体。而以各具者言。则虽只是其一。亦为其全体。何尝只是其统体者为全体乎。主统体者看各具者。则各具者固为其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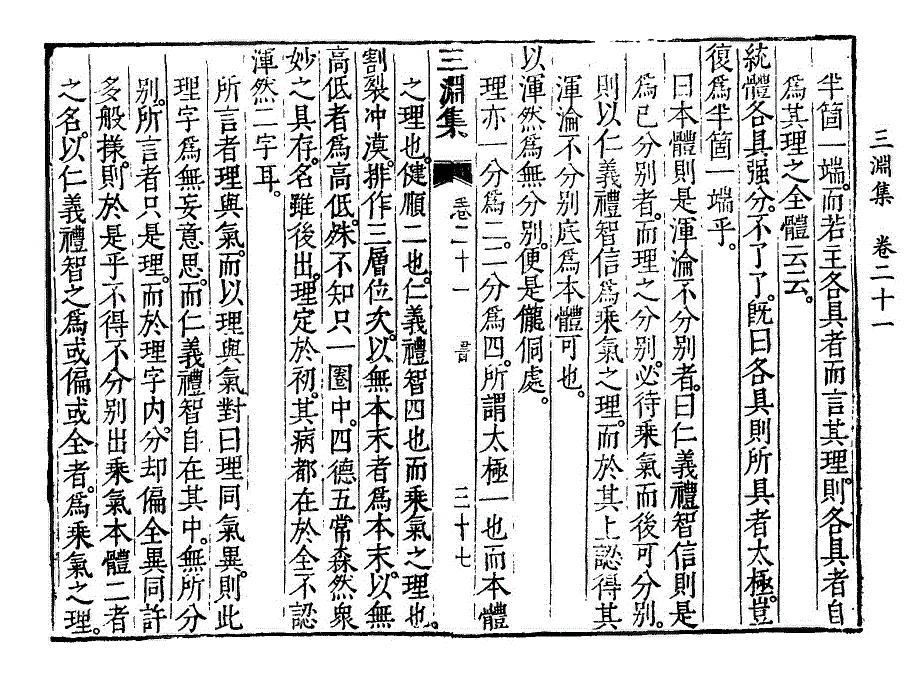 半个一端。而若主各具者而言其理。则各具者自为其理之全体云云。
半个一端。而若主各具者而言其理。则各具者自为其理之全体云云。统体各具强分。不了了。既曰各具则所具者太极。岂复为半个一端乎。
曰本体则是浑沦不分别者。曰仁义礼智信则是为已分别者。而理之分别。必待乘气而后可分别。则以仁义礼智信为乘气之理。而于其上认得其浑沦不分别底为本体可也。
以浑然为无分别。便是儱侗处。
理亦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所谓太极一也而本体之理也。健顺二也。仁义礼智四也而乘气之理也。
割裂冲漠。排作三层位次。以无本末者为本末。以无高低者为高低。殊不知只一圈中。四德五常森然众妙之具存。名虽后出。理定于初。其病都在于全不认浑然二字耳。
所言者理与气。而以理与气对曰理同气异。则此理字为无妄意思。而仁义礼智自在其中。无所分别。所言者只是理。而于理字内。分却偏全异同许多般㨾。则于是乎不得不分别出乘气本体二者之名。以仁义礼智之为或偏或全者。为乘气之理。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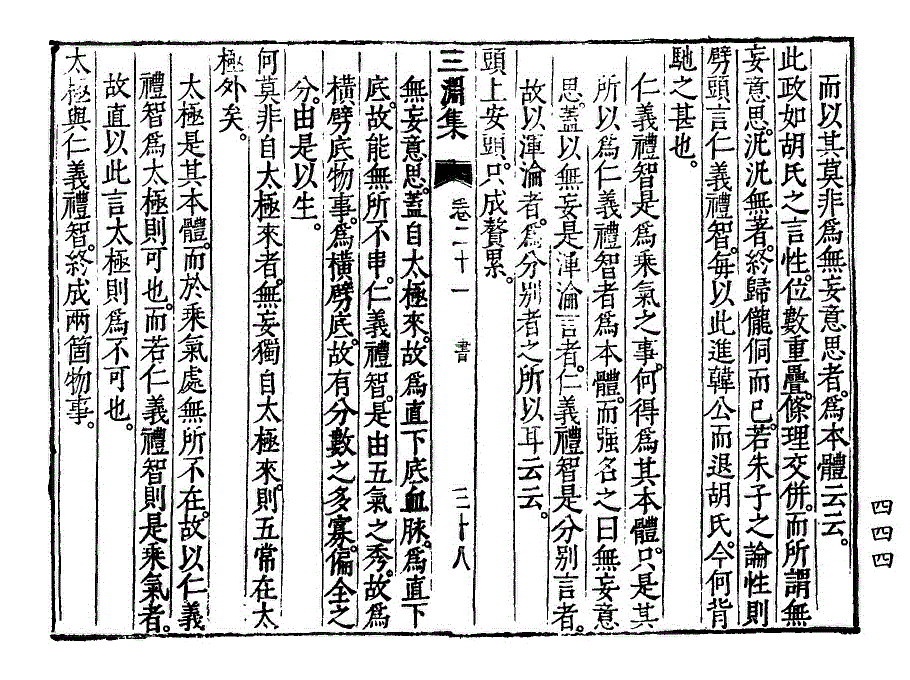 而以其莫非为无妄意思者。为本体云云。
而以其莫非为无妄意思者。为本体云云。此政如胡氏之言性。位数重叠。条理交并。而所谓无妄意思。汎汎无著。终归儱侗而已。若朱子之论性则劈头言仁义礼智。每以此进韩公而退胡氏。今何背驰之甚也。
仁义礼智是为乘气之事。何得为其本体。只是其所以为仁义礼智者为本体。而强名之曰无妄意思。盖以无妄是浑沦言者。仁义礼智是分别言者。故以浑沦者。为分别者之所以耳云云。
头上安头。只成赘累。
无妄意思。盖自太极来。故为直下底血脉。为直下底。故能无所不串。仁义礼智。是由五气之秀。故为横劈底物事。为横劈底。故有分数之多寡。偏全之分。由是以生。
何莫非自太极来者。无妄独自太极来。则五常在太极外矣。
太极是其本体。而于乘气处无所不在。故以仁义礼智为太极则可也。而若仁义礼智则是乘气者。故直以此言太极则为不可也。
太极与仁义礼智。终成两个物事。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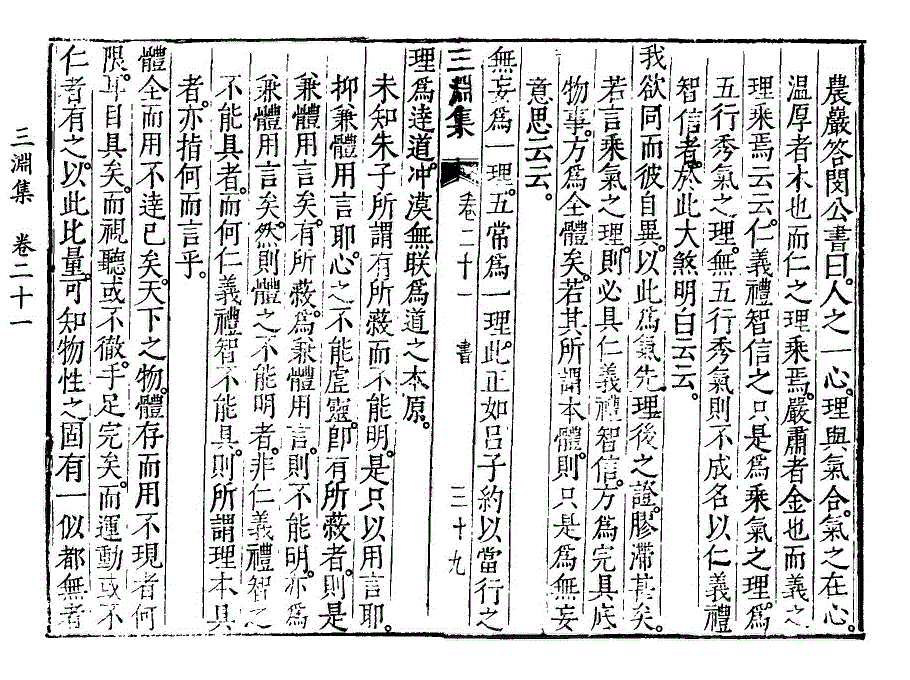 农岩答闵公书曰。人之一心。理与气合。气之在心。温厚者木也而仁之理乘焉。严肃者金也而义之理乘焉云云。仁义礼智信之只是为乘气之理。为五行秀气之理。无五行秀气则不成名以仁义礼智信者。于此大煞明白云云。
农岩答闵公书曰。人之一心。理与气合。气之在心。温厚者木也而仁之理乘焉。严肃者金也而义之理乘焉云云。仁义礼智信之只是为乘气之理。为五行秀气之理。无五行秀气则不成名以仁义礼智信者。于此大煞明白云云。我欲同而彼自异。以此为气先理后之證。胶滞甚矣。
若言乘气之理。则必具仁义礼智信。方为完具底物事。方为全体矣。若其所谓本体。则只是为无妄意思云云。
无妄为一理。五常为一理。此正如吕子约以当行之理为达道。冲漠无眹为道之本原。
未知朱子所谓有所蔽而不能明。是只以用言耶。抑兼体用言耶。心之不能虚灵。即有所蔽者。则是兼体用言矣。有所蔽。为兼体用言。则不能明。亦为兼体用言矣。然则体之不能明者。非仁义礼智之不能具者。而何仁义礼智不能具。则所谓理本具者。亦指何而言乎。
体全而用不达已矣。天下之物。体存而用不现者何限。耳目具矣。而视听或不彻。手足完矣。而运动或不仁者有之。以此比量。可知物性之固有一似都无者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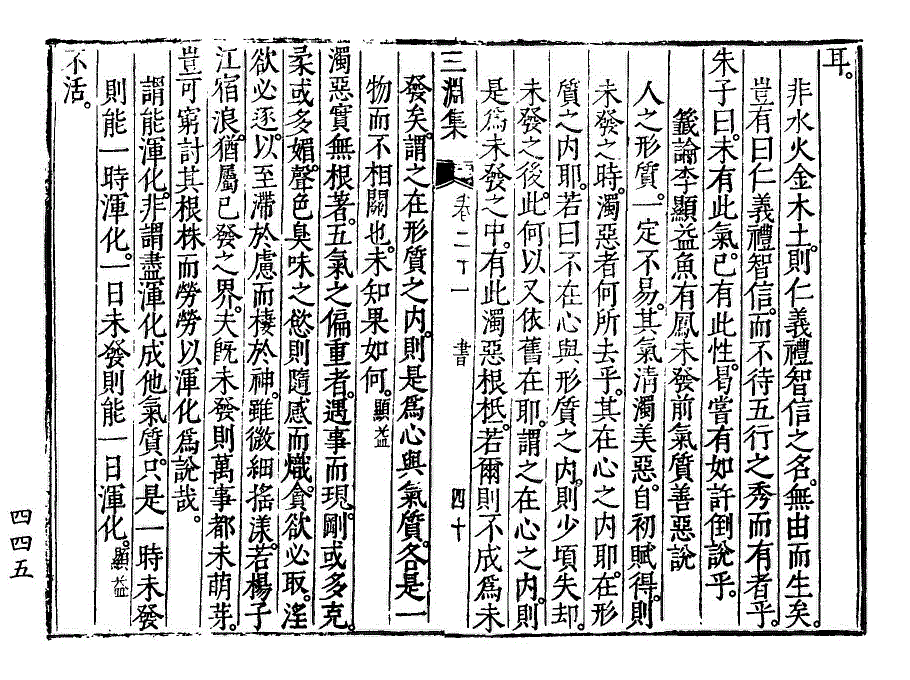 耳。
耳。非水火金木土。则仁义礼智信之名。无由而生矣。岂有曰仁义礼智信。而不待五行之秀而有者乎。
朱子曰。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曷尝有如许倒说乎。
签论李显益鱼有凤未发前气质善恶说
人之形质。一定不易。其气清浊美恶。自初赋得。则未发之时。浊恶者何所去乎。其在心之内耶。在形质之内耶。若曰不在心与形质之内。则少顷失却。未发之后。此何以又依旧在耶。谓之在心之内。则是为未发之中。有此浊恶根柢。若尔则不成为未发矣。谓之在形质之内。则是为心与气质。各是一物而不相关也。未知果如何。(显益)
浊恶实无根著。五气之偏重者。遇事而现。刚或多克。柔或多媚。声色臭味之欲则随感而炽。贪欲必取。淫欲必逐。以至滞于虑而栖于神。虽微细摇漾。若杨子江宿浪。犹属已发之界。夫既未发则万事都未萌芽。岂可穷讨其根株而劳劳以浑化为说哉。
谓能浑化。非谓尽浑化成他气质。只是一时未发则能一时浑化。一日未发则能一日浑化。(显益)
不活。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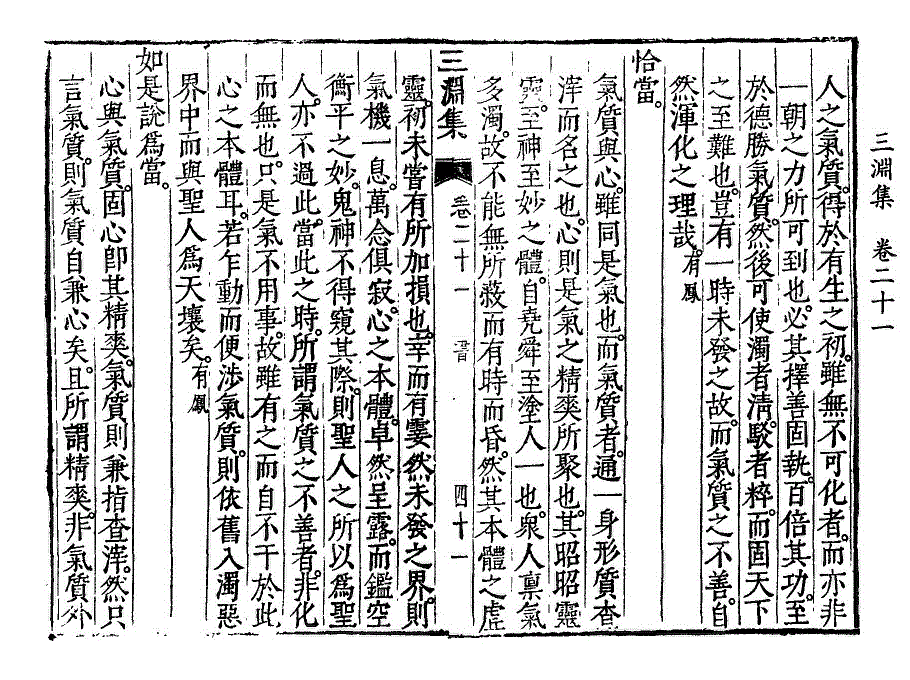 人之气质。得于有生之初。虽无不可化者。而亦非一朝之力所可到也。必其择善固执。百倍其功。至于德胜气质。然后可使浊者清。驳者粹。而固天下之至难也。岂有一时未发之故。而气质之不善。自然浑化之理哉。(有凤)
人之气质。得于有生之初。虽无不可化者。而亦非一朝之力所可到也。必其择善固执。百倍其功。至于德胜气质。然后可使浊者清。驳者粹。而固天下之至难也。岂有一时未发之故。而气质之不善。自然浑化之理哉。(有凤)恰当。
气质与心。虽同是气也。而气质者。通一身形质查滓而名之也。心则是气之精爽所聚也。其昭昭灵灵。至神至妙之体。自尧舜至涂人一也。众人禀气多浊。故不能无所蔽而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虚灵。初未尝有所加损也。幸而有霎然未发之界。则气机一息。万念俱寂。心之本体。卓然呈露。而鉴空衡平之妙。鬼神不得窥其际。则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亦不过此。当此之时。所谓气质之不善者。非化而无也。只是气不用事。故虽有之而自不干于此心之本体耳。若乍动而便涉气质。则依旧入浊恶界中而与圣人为天壤矣。(有凤)
如是说为当。
心与气质。固心即其精爽。气质则兼指查滓。然只言气质。则气质自兼心矣。且所谓精爽。非气质外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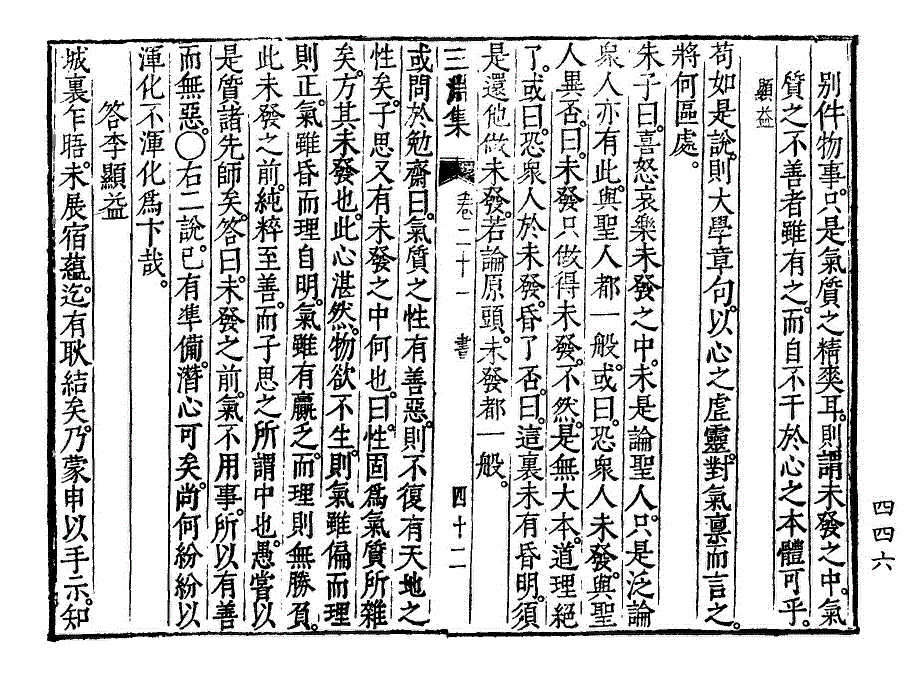 别件物事。只是气质之精爽耳。则谓未发之中。气质之不善者虽有之。而自不干于心之本体可乎。(显益)
别件物事。只是气质之精爽耳。则谓未发之中。气质之不善者虽有之。而自不干于心之本体可乎。(显益)苟如是说。则大学章句。以心之虚灵。对气禀而言之。将何区处。
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或曰。恐众人未发。与圣人异否。曰。未发只做得未发。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或曰。恐众人于未发。昏了否。曰。这里未有昏明。须是还他做未发。若论原头。未发都一般。
或问于勉斋曰。气质之性有善恶。则不复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又有未发之中何也。曰。性固为气质所杂矣。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理则正。气虽昏而理自明。气虽有赢乏。而理则无胜负。此未发之前。纯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谓中也。愚尝以是质诸先师矣。答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右二说。已有准备。潜心可矣。尚何纷纷以浑化不浑化为卞哉。
答李显益
城里乍晤。未展宿蕴。迄有耿结矣。乃蒙申以手示。知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7H 页
 住近寺。披悉辞旨。便欲欣然从之矣。翕归自松楸。得病非细。外感与下泄并作。殆不自振。殊闷殊闷。承谕。欲从事乎上蔡延平。简严旨诀。自择之审。似为得当。恐不必以偏落为虑。且大居敬而贵穷理。即上蔡之所自道。而延平亦非偏于心学者。其不快于和靖体用显微之云。大启朱子之密察。岂不为两足尊乎。敢请勿前郤。试下一二年工夫如何。见投新图。病昏未暇阅。虽使著神覆绎。恐未必融契澜漫。徒为诤閧之归。于高明默澄初功。大有搅混为非便。拈此白完。幸勿咎太简如何。千万扶头艰复。不能细究。
住近寺。披悉辞旨。便欲欣然从之矣。翕归自松楸。得病非细。外感与下泄并作。殆不自振。殊闷殊闷。承谕。欲从事乎上蔡延平。简严旨诀。自择之审。似为得当。恐不必以偏落为虑。且大居敬而贵穷理。即上蔡之所自道。而延平亦非偏于心学者。其不快于和靖体用显微之云。大启朱子之密察。岂不为两足尊乎。敢请勿前郤。试下一二年工夫如何。见投新图。病昏未暇阅。虽使著神覆绎。恐未必融契澜漫。徒为诤閧之归。于高明默澄初功。大有搅混为非便。拈此白完。幸勿咎太简如何。千万扶头艰复。不能细究。答朴弼周
日昨惠枉。荷意之勤。亦有清规所以矫轻警惰者为多。耿耿在念。倾注益深矣。复此巍牍之辱。益见相与之意非寻常论交者可比。至于称许陈义之过当。则非区区所及也。惭骍靡容而已。示谕寡欲之说。昨所未契。蒙此申扣。政所谓辨不明不措者也。讲贯切偲之道。当如是矣。顾此荒昏废业。偶陈先入之说。未保其能免纰缪。而伊后忧遑。未及参考其原注以求会同焉矣。承谕若堕杳茫。不知所以为复。但据人所不能无五字而论之。则恐是如人心之说者。通圣凡而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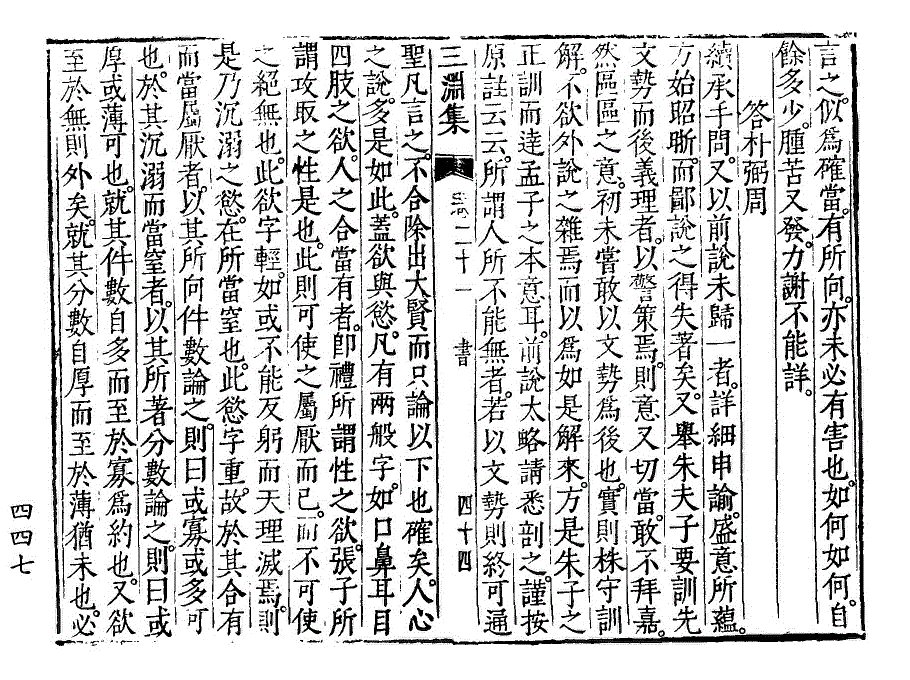 言之。似为确当。有所向。亦未必有害也。如何如何。自馀多少。肿苦又发。力谢不能详。
言之。似为确当。有所向。亦未必有害也。如何如何。自馀多少。肿苦又发。力谢不能详。答朴弼周
续承手问。又以前说未归一者。详细申谕。盛意所蕴。方始昭晢。而鄙说之得失著矣。又举朱夫子要训先文势而后义理者。以警策焉。则意又切当。敢不拜嘉。然区区之意。初未尝敢以文势为后也。实则株守训解。不欲外说之杂焉而以为如是解来。方是朱子之正训而达孟子之本意耳。前说太略请悉剖之。谨按原注云云。所谓人所不能无者。若以文势则终可通圣凡言之。不合除出大贤而只论以下也确矣。人心之说。多是如此。盖欲与欲。凡有两般字。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人之合当有者。即礼所谓性之欲。张子所谓攻取之性是也。此则可使之属厌而已。而不可使之绝无也。此欲字轻。如或不能反躬而天理灭焉。则是乃沉溺之欲。在所当窒也。此欲字重。故于其合有而当属厌者。以其所向件数论之。则曰或寡或多可也。于其沉溺而当窒者。以其所著分数论之。则曰或厚或薄可也。就其件数自多而至于寡为约也。又欲至于无则外矣。就其分数自厚而至于薄犹未也。必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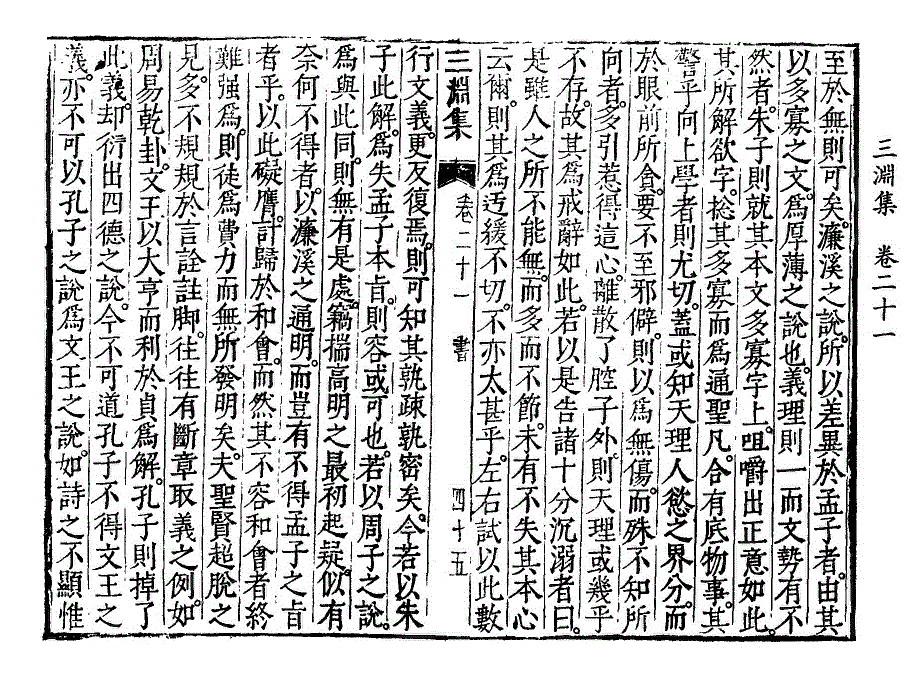 至于无则可矣。濂溪之说。所以差异于孟子者。由其以多寡之文。为厚薄之说也。义理则一而文势有不然者。朱子则就其本文多寡字上。咀嚼出正意如此。其所解欲字。总其多寡而为通圣凡。合有底物事。其警乎向上学者则尤切。盖或知天理人欲之界分。而于眼前所贪。要不至邪僻。则以为无伤。而殊不知所向者。多引惹得这心。离散了腔子外。则天理或几乎不存。故其为戒辞如此。若以是告诸十分沉溺者曰。是虽人之所不能无。而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云尔。则其为迂缓不切。不亦太甚乎。左右试以此数行文义。更反复焉。则可知其孰疏孰密矣。今若以朱子此解。为失孟子本旨。则容或可也。若以周子之说。为与此同。则无有是处。窃揣高明之最初起疑。似有奈何不得者。以濂溪之通明。而岂有不得孟子之旨者乎。以此碍膺。计归于和会。而然其不容和会者终难强为。则徒为费力而无所发明矣。夫圣贤超脱之见。多不规规于言诠注脚。往往有断章取义之例。如周易乾卦。文王以大亨而利于贞为解。孔子则掉了此义。却衍出四德之说。今不可道孔子不得文王之义。亦不可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如诗之不显惟
至于无则可矣。濂溪之说。所以差异于孟子者。由其以多寡之文。为厚薄之说也。义理则一而文势有不然者。朱子则就其本文多寡字上。咀嚼出正意如此。其所解欲字。总其多寡而为通圣凡。合有底物事。其警乎向上学者则尤切。盖或知天理人欲之界分。而于眼前所贪。要不至邪僻。则以为无伤。而殊不知所向者。多引惹得这心。离散了腔子外。则天理或几乎不存。故其为戒辞如此。若以是告诸十分沉溺者曰。是虽人之所不能无。而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云尔。则其为迂缓不切。不亦太甚乎。左右试以此数行文义。更反复焉。则可知其孰疏孰密矣。今若以朱子此解。为失孟子本旨。则容或可也。若以周子之说。为与此同。则无有是处。窃揣高明之最初起疑。似有奈何不得者。以濂溪之通明。而岂有不得孟子之旨者乎。以此碍膺。计归于和会。而然其不容和会者终难强为。则徒为费力而无所发明矣。夫圣贤超脱之见。多不规规于言诠注脚。往往有断章取义之例。如周易乾卦。文王以大亨而利于贞为解。孔子则掉了此义。却衍出四德之说。今不可道孔子不得文王之义。亦不可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如诗之不显惟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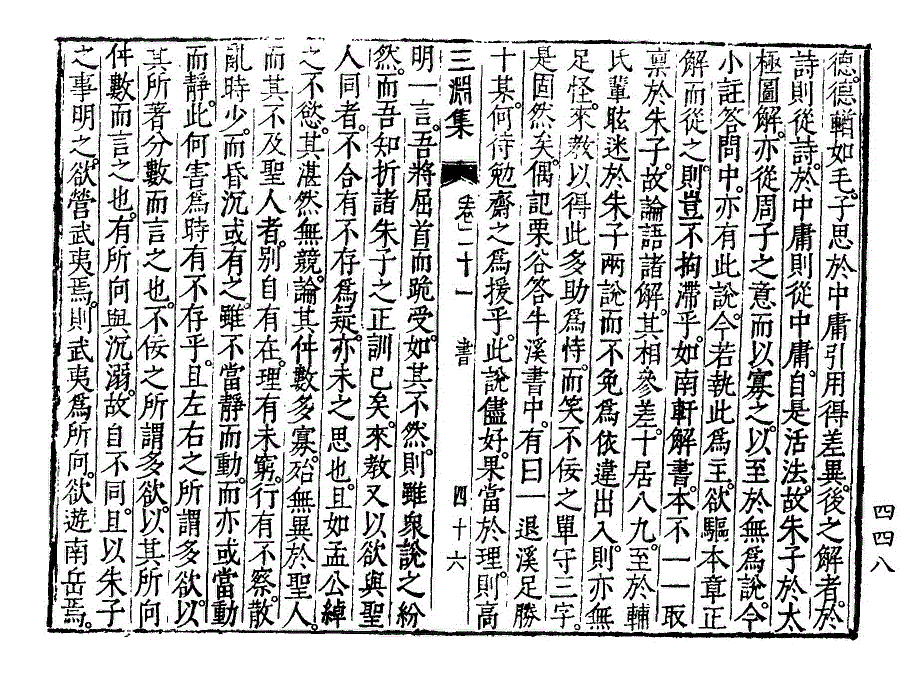 德。德輶如毛。子思于中庸引用得差异。后之解者。于诗则从诗。于中庸则从中庸。自是活法。故朱子于太极图解。亦从周子之意而以寡之。以至于无为说。今小注答问中。亦有此说。今若执此为主。欲驱本章正解而从之。则岂不拘滞乎。如南轩解书。本不一一取禀于朱子。故论语诸解。其相参差。十居八九。至于辅氏辈眩迷于朱子两说而不免为依违出入。则亦无足怪。来教以得此多助为恃。而笑不佞之单守三字。是固然矣。偶记栗谷答牛溪书中。有曰一退溪足胜十某。何待勉斋之为援乎。此说尽好。果当于理。则高明一言。吾将屈首而跪受。如其不然。则虽众说之纷然。而吾知折诸朱子之正训已矣。来教又以欲与圣人同者。不合有不存为疑。亦未之思也。且如孟公绰之不欲。其湛然无竞。论其件数多寡。殆无异于圣人。而其不及圣人者。别自有在。理有未穷。行有不察。散乱时少。而昏沉或有之。虽不当静而动。而亦或当动而静。此何害为时有不存乎。且左右之所谓多欲。以其所著分数而言之也。不佞之所谓多欲。以其所向件数而言之也。有所向与沉溺。故自不同。且以朱子之事明之。欲营武夷焉。则武夷为所向。欲游南岳焉。
德。德輶如毛。子思于中庸引用得差异。后之解者。于诗则从诗。于中庸则从中庸。自是活法。故朱子于太极图解。亦从周子之意而以寡之。以至于无为说。今小注答问中。亦有此说。今若执此为主。欲驱本章正解而从之。则岂不拘滞乎。如南轩解书。本不一一取禀于朱子。故论语诸解。其相参差。十居八九。至于辅氏辈眩迷于朱子两说而不免为依违出入。则亦无足怪。来教以得此多助为恃。而笑不佞之单守三字。是固然矣。偶记栗谷答牛溪书中。有曰一退溪足胜十某。何待勉斋之为援乎。此说尽好。果当于理。则高明一言。吾将屈首而跪受。如其不然。则虽众说之纷然。而吾知折诸朱子之正训已矣。来教又以欲与圣人同者。不合有不存为疑。亦未之思也。且如孟公绰之不欲。其湛然无竞。论其件数多寡。殆无异于圣人。而其不及圣人者。别自有在。理有未穷。行有不察。散乱时少。而昏沉或有之。虽不当静而动。而亦或当动而静。此何害为时有不存乎。且左右之所谓多欲。以其所著分数而言之也。不佞之所谓多欲。以其所向件数而言之也。有所向与沉溺。故自不同。且以朱子之事明之。欲营武夷焉。则武夷为所向。欲游南岳焉。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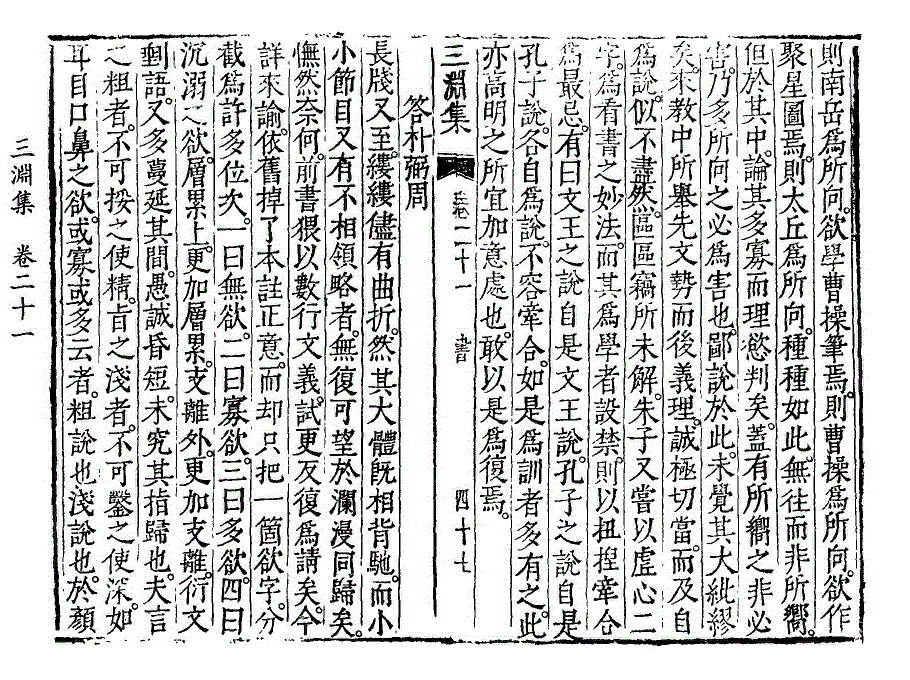 则南岳为所向。欲学曹操笔焉。则曹操为所向。欲作聚星图焉。则太丘为所向。种种如此。无往而非所向。但于其中。论其多寡而理欲判矣。盖有所向之非必害。乃多所向之必为害也。鄙说于此。未觉其大纰缪矣。来教中所举先文势而后义理。诚极切当。而及自为说。似不尽然。区区窃所未解。朱子又尝以虚心二字。为看书之妙法。而其为学者设禁。则以扭捏牵合为最忌。有曰文王之说自是文王说。孔子之说自是孔子说。各自为说。不容牵合。如是为训者多有之。此亦高明之所宜加意处也。敢以是为复焉。
则南岳为所向。欲学曹操笔焉。则曹操为所向。欲作聚星图焉。则太丘为所向。种种如此。无往而非所向。但于其中。论其多寡而理欲判矣。盖有所向之非必害。乃多所向之必为害也。鄙说于此。未觉其大纰缪矣。来教中所举先文势而后义理。诚极切当。而及自为说。似不尽然。区区窃所未解。朱子又尝以虚心二字。为看书之妙法。而其为学者设禁。则以扭捏牵合为最忌。有曰文王之说自是文王说。孔子之说自是孔子说。各自为说。不容牵合。如是为训者多有之。此亦高明之所宜加意处也。敢以是为复焉。答朴弼周
长笺又至。缕缕尽有曲折。然其大体既相背驰。而小小节目又有不相领略者。无复可望于澜漫同归矣。怃然奈何。前书猥以数行文义。试更反复为请矣。今详来谕。依旧掉了本注正意。而却只把一个欲字。分截为许多位次。一曰无欲。二曰寡欲。三曰多欲。四曰沉溺之欲。层累上。更加层累。支离外。更加支离。衍文剩语。又多蔓延其间。愚诚昏短。未究其指归也。夫言之粗者。不可挼之使精。旨之浅者。不可凿之使深。如耳目口鼻之欲。或寡或多云者。粗说也浅说也。于颜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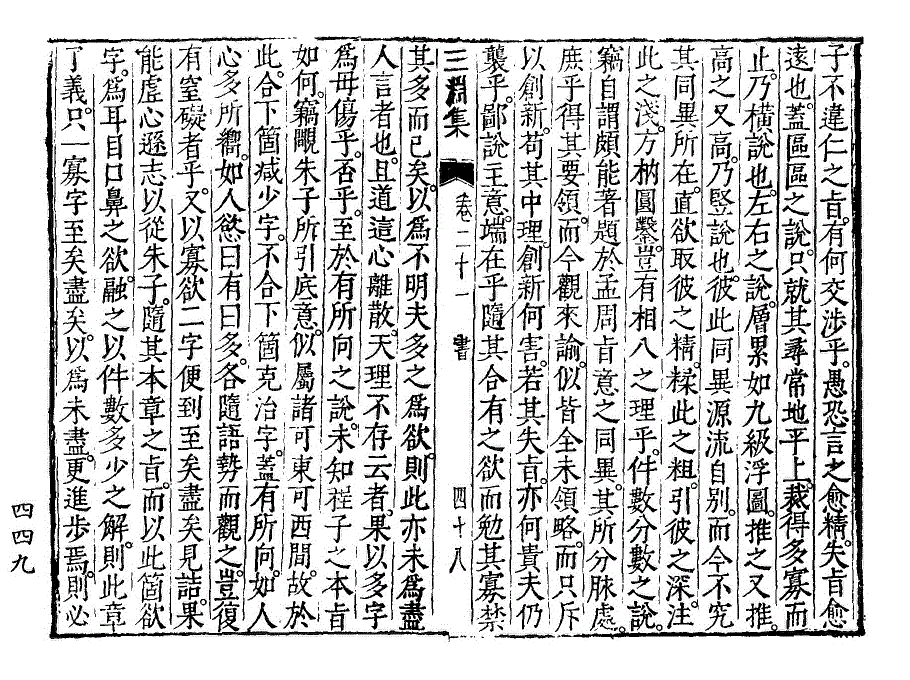 子不违仁之旨。有何交涉乎。愚恐言之愈精。失旨愈远也。盖区区之说。只就其寻常地平上。裁得多寡而止。乃横说也。左右之说。层累如九级浮图。推之又推。高之又高。乃竖说也。彼此同异源流自别。而今不究其同异所在。直欲取彼之精。糅此之粗。引彼之深。注此之浅。方枘圆凿。岂有相入之理乎。件数分数之说。窃自谓颇能著题于孟周旨意之同异。其所分脉处。庶乎得其要领。而今观来谕。似皆全未领略。而只斥以创新。苟其中理。创新何害。若其失旨。亦何贵夫仍袭乎。鄙说主意。端在乎随其合有之欲而勉其寡禁其多而已矣。以为不明夫多之为欲。则此亦未为尽人言者也。且道这心离散。天理不存云者。果以多字为毋伤乎。否乎。至于有所向之说。未知程子之本旨如何。窃覵朱子所引底意。似属诸可东可西间。故于此。合下个减少字。不合下个克治字。盖有所向。如人心多所向。如人欲曰有曰多。各随语势而观之。岂复有窒碍者乎。又以寡欲二字便到至矣尽矣见诘。果能虚心逊志以从朱子。随其本章之旨。而以此个欲字。为耳目口鼻之欲。融之以件数多少之解。则此章了义。只一寡字至矣尽矣。以为未尽。更进步焉。则必
子不违仁之旨。有何交涉乎。愚恐言之愈精。失旨愈远也。盖区区之说。只就其寻常地平上。裁得多寡而止。乃横说也。左右之说。层累如九级浮图。推之又推。高之又高。乃竖说也。彼此同异源流自别。而今不究其同异所在。直欲取彼之精。糅此之粗。引彼之深。注此之浅。方枘圆凿。岂有相入之理乎。件数分数之说。窃自谓颇能著题于孟周旨意之同异。其所分脉处。庶乎得其要领。而今观来谕。似皆全未领略。而只斥以创新。苟其中理。创新何害。若其失旨。亦何贵夫仍袭乎。鄙说主意。端在乎随其合有之欲而勉其寡禁其多而已矣。以为不明夫多之为欲。则此亦未为尽人言者也。且道这心离散。天理不存云者。果以多字为毋伤乎。否乎。至于有所向之说。未知程子之本旨如何。窃覵朱子所引底意。似属诸可东可西间。故于此。合下个减少字。不合下个克治字。盖有所向。如人心多所向。如人欲曰有曰多。各随语势而观之。岂复有窒碍者乎。又以寡欲二字便到至矣尽矣见诘。果能虚心逊志以从朱子。随其本章之旨。而以此个欲字。为耳目口鼻之欲。融之以件数多少之解。则此章了义。只一寡字至矣尽矣。以为未尽。更进步焉。则必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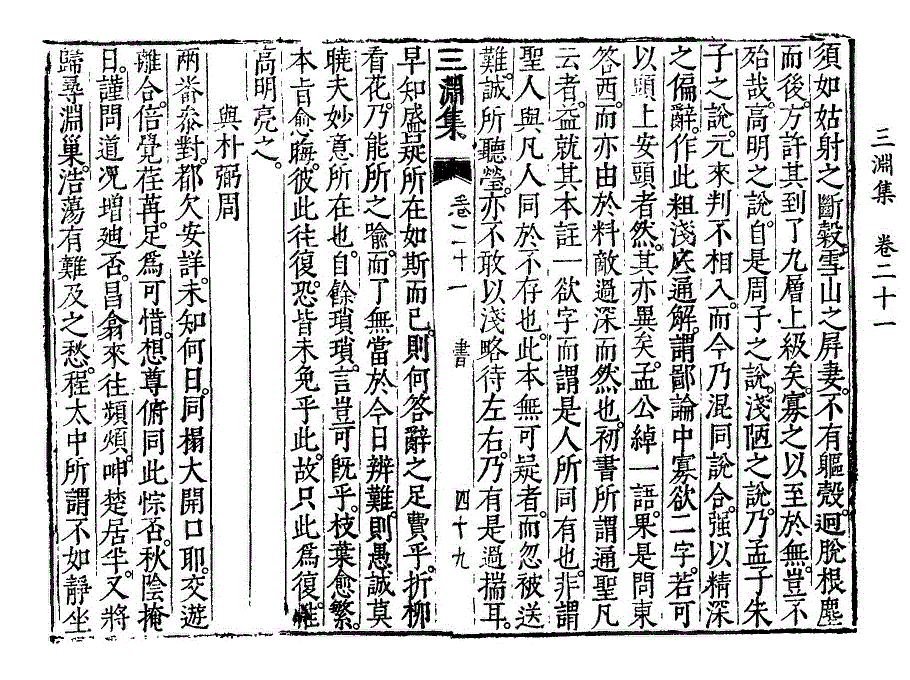 须如姑射之断谷。雪山之屏妻。不有躯壳。迥脱根尘而后。方许其到了九层上级矣。寡之以至于无。岂不殆哉。高明之说。自是周子之说。浅陋之说。乃孟子朱子之说。元来判不相入。而今乃混同说合。强以精深之偏辞。作此粗浅底通解。谓鄙论中寡欲二字。若可以头上安头者然。其亦异矣。孟公绰一语。果是问东答西。而亦由于料敌过深而然也。初书所谓通圣凡云者。益就其本注一欲字而谓是人所同有也。非谓圣人与凡人同于不存也。此本无可疑者。而忽被送难。诚所听莹。亦不敢以浅略待左右。乃有是过揣耳。早知盛疑所在如斯而已。则何答辞之足费乎。折柳看花。乃能所之喻。而了无当于今日辨难。则愚诚莫晓夫妙意所在也。自馀琐琐。言岂可既乎。枝叶愈繁。本旨愈晦。彼此往复。恐皆未免乎此。故只此为复。惟高明亮之。
须如姑射之断谷。雪山之屏妻。不有躯壳。迥脱根尘而后。方许其到了九层上级矣。寡之以至于无。岂不殆哉。高明之说。自是周子之说。浅陋之说。乃孟子朱子之说。元来判不相入。而今乃混同说合。强以精深之偏辞。作此粗浅底通解。谓鄙论中寡欲二字。若可以头上安头者然。其亦异矣。孟公绰一语。果是问东答西。而亦由于料敌过深而然也。初书所谓通圣凡云者。益就其本注一欲字而谓是人所同有也。非谓圣人与凡人同于不存也。此本无可疑者。而忽被送难。诚所听莹。亦不敢以浅略待左右。乃有是过揣耳。早知盛疑所在如斯而已。则何答辞之足费乎。折柳看花。乃能所之喻。而了无当于今日辨难。则愚诚莫晓夫妙意所在也。自馀琐琐。言岂可既乎。枝叶愈繁。本旨愈晦。彼此往复。恐皆未免乎此。故只此为复。惟高明亮之。与朴弼周
两番参对。都欠安详。未知何日。同榻大开口耶。交游离合。倍觉荏苒。足为可惜。想尊俯同此悰否。秋阴掩日。谨问道况增迪否。昌翕来往频烦。呻楚居半。又将归寻渊巢。浩荡有难及之愁。程太中所谓不如静坐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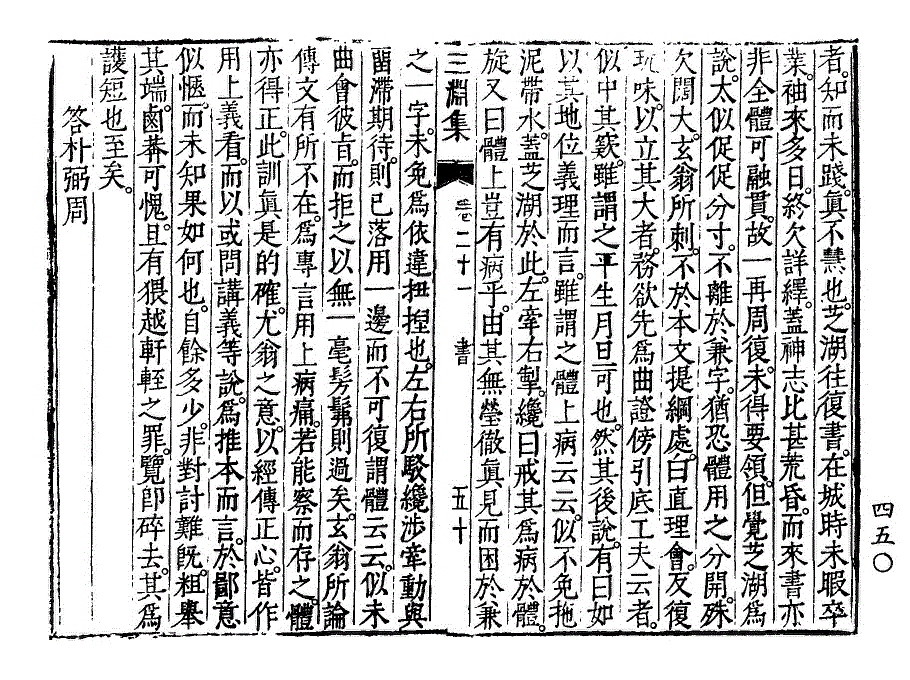 者。知而未践。真不慧也。芝湖往复书。在城时未暇卒业。袖来多日。终欠详绎。盖神志比甚荒昏。而来书亦非全体可融贯。故一再周复。未得要领。但觉芝湖为说。太似促促分寸。不离于兼字。犹恐体用之分开。殊欠阔大。玄翁所刺。不于本文提纲处。白直理会。反复玩味。以立其大者。务欲先为曲證傍引底工夫云者。似中其窾。虽谓之平生月旦可也。然其后说。有曰如以其地位义理而言。虽谓之体上病云云。似不免拖泥带水。盖芝湖于此。左牵右掣。才曰戒其为病于体。旋又曰体上岂有病乎。由其无莹彻真见而困于兼之一字。未免为依违扭捏也。左右所驳才涉牵动与留滞期待。则已落用一边而不可复谓体云云。似未曲会彼旨。而拒之以无一毫髣髴则过矣。玄翁所论传文有所不在。为专言用上病痛。若能察而存之。体亦得正。此训真是的确。尤翁之意。以经传正心。皆作用上义看。而以或问讲义等说。为推本而言。于鄙意似惬。而未知果如何也。自馀多少。非对讨难既。粗举其端。卤莽可愧。且有猥越轩轾之罪。览即碎去。其为护短也至矣。
者。知而未践。真不慧也。芝湖往复书。在城时未暇卒业。袖来多日。终欠详绎。盖神志比甚荒昏。而来书亦非全体可融贯。故一再周复。未得要领。但觉芝湖为说。太似促促分寸。不离于兼字。犹恐体用之分开。殊欠阔大。玄翁所刺。不于本文提纲处。白直理会。反复玩味。以立其大者。务欲先为曲證傍引底工夫云者。似中其窾。虽谓之平生月旦可也。然其后说。有曰如以其地位义理而言。虽谓之体上病云云。似不免拖泥带水。盖芝湖于此。左牵右掣。才曰戒其为病于体。旋又曰体上岂有病乎。由其无莹彻真见而困于兼之一字。未免为依违扭捏也。左右所驳才涉牵动与留滞期待。则已落用一边而不可复谓体云云。似未曲会彼旨。而拒之以无一毫髣髴则过矣。玄翁所论传文有所不在。为专言用上病痛。若能察而存之。体亦得正。此训真是的确。尤翁之意。以经传正心。皆作用上义看。而以或问讲义等说。为推本而言。于鄙意似惬。而未知果如何也。自馀多少。非对讨难既。粗举其端。卤莽可愧。且有猥越轩轾之罪。览即碎去。其为护短也至矣。答朴弼周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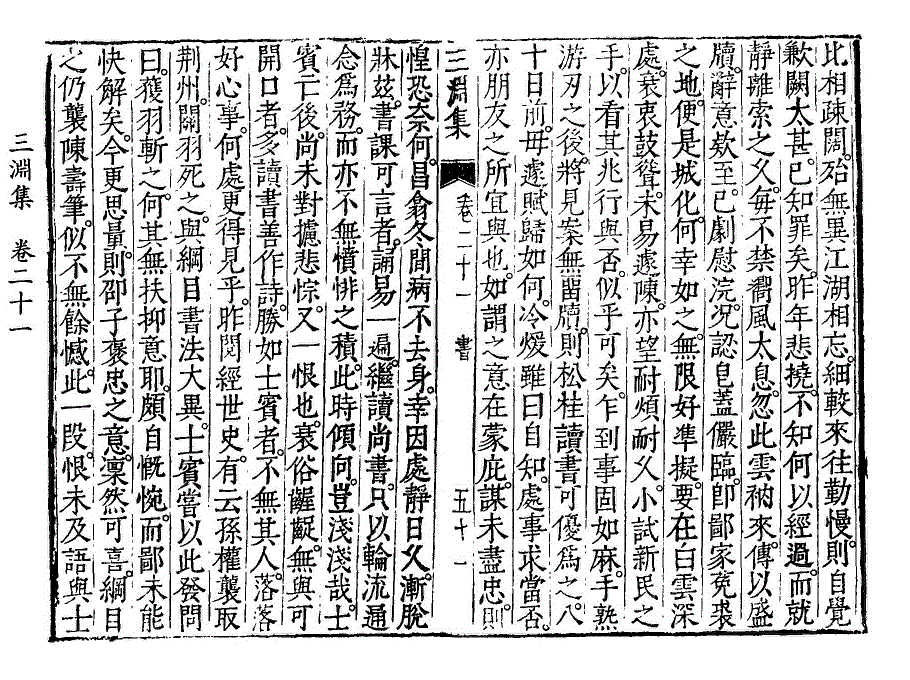 比相疏阔。殆无异江湖相忘。细较来往勤慢。则自觉歉阙太甚。已知罪矣。昨年悲挠。不知何以经过。而就静离索之久。每不禁向风太息。忽此云衲来。传以盛牍。辞意款至。已剧慰浣。况认皂盖俨临。即鄙家菟裘之地。便是城化。何幸如之。无限好准拟。要在白云深处。衰衷鼓耸。未易遽陈。亦望耐烦耐久。小试新民之手。以看其兆行与否。似乎可矣。乍到事固如麻。手熟游刃之后。将见案无留牍。则松桂读书可优为之。八十日前。毋遽赋归如何。冷煖虽曰自知。处事求当否。亦朋友之所宜与也。如谓之意在蒙庇。谋未尽忠。则惶恐奈何。昌翕冬间病不去身。幸因处静日久。渐脱床玆。书课可言者。诵易一遍。继读尚书。只以轮流通念为务。而亦不无愤悱之积。此时倾向。岂浅浅哉。士宾亡后。尚未对摅悲悰。又一恨也。衰俗龌龊。无与可开口者。多读书善作诗。胜如士宾者。不无其人。落落好心事。何处更得见乎。昨阅经世史。有云孙权袭取荆州。关羽死之。与纲目书法大异。士宾尝以此发问曰。获羽斩之。何其无扶抑意耶。颇自慨惋。而鄙未能快解矣。今更思量。则邵子褒忠之意。凛然可喜。纲目之仍袭陈寿笔。似不无馀憾。此一段。恨未及语与士
比相疏阔。殆无异江湖相忘。细较来往勤慢。则自觉歉阙太甚。已知罪矣。昨年悲挠。不知何以经过。而就静离索之久。每不禁向风太息。忽此云衲来。传以盛牍。辞意款至。已剧慰浣。况认皂盖俨临。即鄙家菟裘之地。便是城化。何幸如之。无限好准拟。要在白云深处。衰衷鼓耸。未易遽陈。亦望耐烦耐久。小试新民之手。以看其兆行与否。似乎可矣。乍到事固如麻。手熟游刃之后。将见案无留牍。则松桂读书可优为之。八十日前。毋遽赋归如何。冷煖虽曰自知。处事求当否。亦朋友之所宜与也。如谓之意在蒙庇。谋未尽忠。则惶恐奈何。昌翕冬间病不去身。幸因处静日久。渐脱床玆。书课可言者。诵易一遍。继读尚书。只以轮流通念为务。而亦不无愤悱之积。此时倾向。岂浅浅哉。士宾亡后。尚未对摅悲悰。又一恨也。衰俗龌龊。无与可开口者。多读书善作诗。胜如士宾者。不无其人。落落好心事。何处更得见乎。昨阅经世史。有云孙权袭取荆州。关羽死之。与纲目书法大异。士宾尝以此发问曰。获羽斩之。何其无扶抑意耶。颇自慨惋。而鄙未能快解矣。今更思量。则邵子褒忠之意。凛然可喜。纲目之仍袭陈寿笔。似不无馀憾。此一段。恨未及语与士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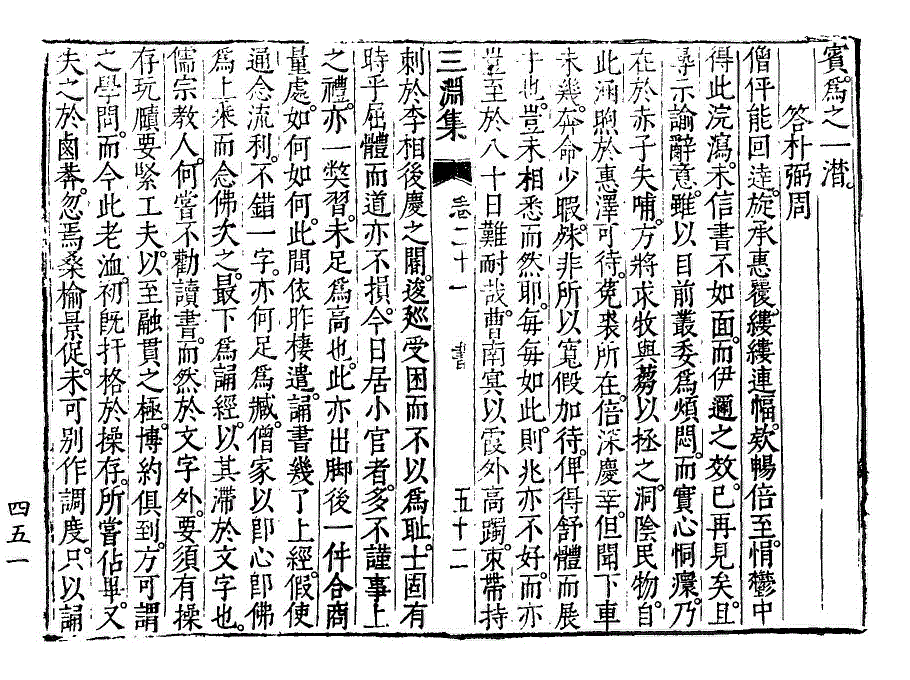 宾。为之一潸。
宾。为之一潸。答朴弼周
僧伻能回达。旋承惠覆。缕缕连幅。款畅倍至。悁郁中得此浣泻。未信书不如面。而伊迩之效。已再见矣。且寻示谕辞意。虽以目前丛委为烦闷。而实心恫瘝。乃在于赤子失哺。方将求牧与刍以拯之。洞阴民物。自此涵煦于惠泽可待。菟裘所在。倍深庆幸。但闻下车未几。奔命少暇。殊非所以宽假加待。俾得舒体而展手也。岂未相悉而然耶。每每如此。则兆亦不好。而亦岂至于八十日难耐哉。曹南冥以霞外高躅。束带持刺于李相后庆之阍。逡巡受困而不以为耻。士固有时乎屈体而道亦不损。今日居小官者。多不谨事上之礼。亦一弊习。未足为高也。此亦出脚后一件合商量处。如何如何。此间依昨栖遣。诵书几了上经。假使通念流利。不错一字。亦何足为臧。僧家以即心即佛为上乘而念佛次之。最下为诵经。以其滞于文字也。儒宗教人。何尝不劝读书。而然于文字外。要须有操存玩赜要紧工夫。以至融贯之极。博约俱到。方可谓之学问。而今此老洫。初既捍格于操存。所尝佔毕。又失之于卤莽。忽焉桑榆景促。未可别作调度。只以诵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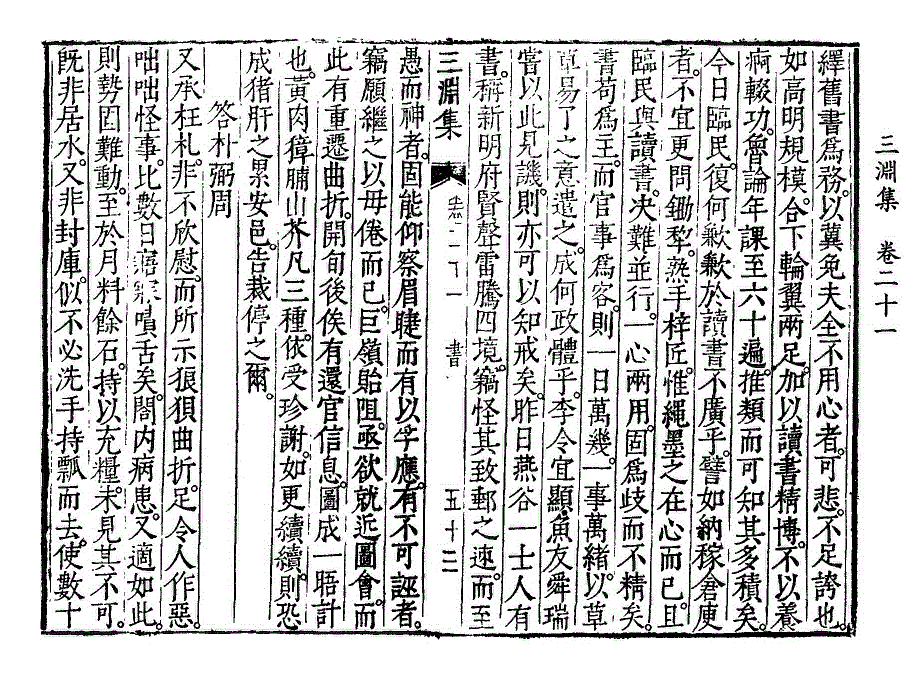 绎旧书为务。以冀免夫全不用心者。可悲。不足誇也。如高明规模。合下轮翼两足。加以读书精博。不以养痾辍功。鲁论年课至六十遍。推类而可知其多积矣。今日临民。复何歉歉于读书不广乎。譬如纳稼仓庾者。不宜更问锄犁。熟手梓匠。惟绳墨之在心而已。且临民与读书。决难并行。一心两用。固为歧而不精矣。书苟为主。而官事为客。则一日万几。一事万绪。以草草易了之意遣之。成何政体乎。李令宜显,鱼友舜瑞尝以此见讥。则亦可以知戒矣。昨日燕谷一士人有书。称新明府贤声雷腾四境。窃怪其致邮之速。而至愚而神者。固能仰察眉睫而有以孚应。有不可诬者。窃愿继之以毋倦而已。巨岭贻阻。亟欲就近图会。而此有重迁曲折。开旬后俟有还官信息。图成一晤计也。黄肉獐脯山芥凡三种。依受珍谢。如更续续。则恐成猪肝之累安邑。告裁停之尔。
绎旧书为务。以冀免夫全不用心者。可悲。不足誇也。如高明规模。合下轮翼两足。加以读书精博。不以养痾辍功。鲁论年课至六十遍。推类而可知其多积矣。今日临民。复何歉歉于读书不广乎。譬如纳稼仓庾者。不宜更问锄犁。熟手梓匠。惟绳墨之在心而已。且临民与读书。决难并行。一心两用。固为歧而不精矣。书苟为主。而官事为客。则一日万几。一事万绪。以草草易了之意遣之。成何政体乎。李令宜显,鱼友舜瑞尝以此见讥。则亦可以知戒矣。昨日燕谷一士人有书。称新明府贤声雷腾四境。窃怪其致邮之速。而至愚而神者。固能仰察眉睫而有以孚应。有不可诬者。窃愿继之以毋倦而已。巨岭贻阻。亟欲就近图会。而此有重迁曲折。开旬后俟有还官信息。图成一晤计也。黄肉獐脯山芥凡三种。依受珍谢。如更续续。则恐成猪肝之累安邑。告裁停之尔。答朴弼周
又承枉札。非不欣慰。而所示狼狈曲折。足令人作恶。咄咄怪事。比数日寤寐啧舌矣。閤内病患。又适如此。则势固难动。至于月料馀石。持以充粮。未见其不可。既非居水。又非封库。似不必洗手持瓢而去。使数十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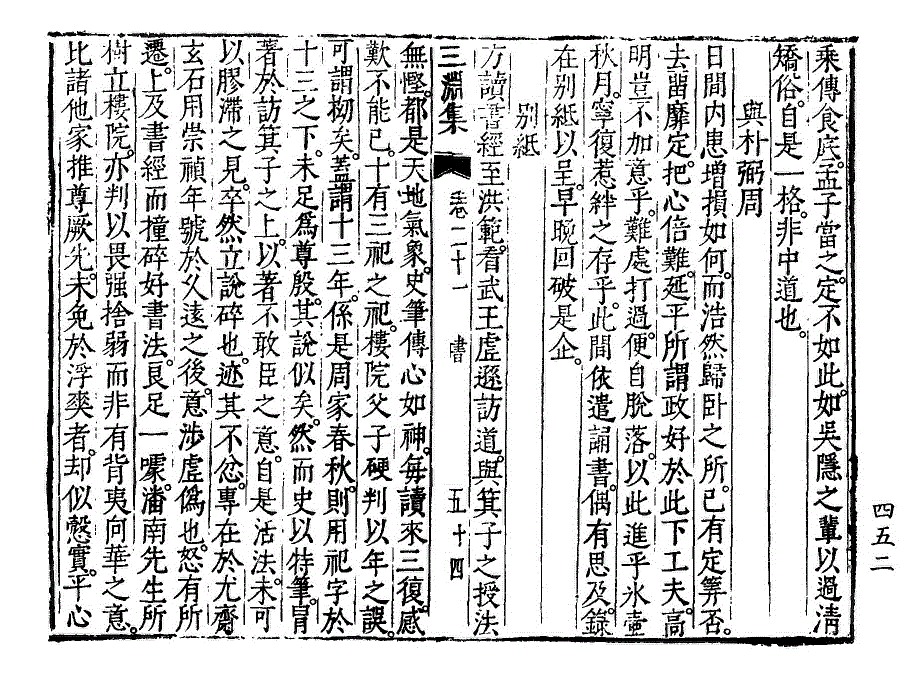 乘传食底。孟子当之。定不如此。如吴隐之辈以过清矫俗。自是一格。非中道也。
乘传食底。孟子当之。定不如此。如吴隐之辈以过清矫俗。自是一格。非中道也。与朴弼周
日间内患增损如何。而浩然归卧之所。已有定算否。去留靡定。把心倍难。延平所谓政好于此下工夫。高明岂不加意乎。难处打过。便自脱落。以此进乎冰壶秋月。宁复惹绊之存乎。此间依遣诵书。偶有思及。录在别纸以呈。早晚回破是企。
别纸
方读书经至洪范。看武王虚逊访道。与箕子之授法无悭。都是天地气象。史笔传心如神。每读来三复。感叹不能已。十有三祀之祀。楼院父子硬判以年之误。可谓拗矣。盖谓十三年。系是周家春秋。则用祀字于十三之下。未足为尊殷。其说似矣。然而史以特笔。冒著于访箕子之上。以著不敢臣之意。自是活法。未可以胶滞之见。卒然立说碎也。迹其不忿。专在于尤斋,玄石用崇祯年号于久远之后。意涉虚伪也。怒有所迁。上及书经而撞碎好书法。良足一噱。潘南先生所树立楼院。亦判以畏强舍弱而非有背夷向华之意。比诸他家推尊厥先。未免于浮爽者。却似悫实。平心
三渊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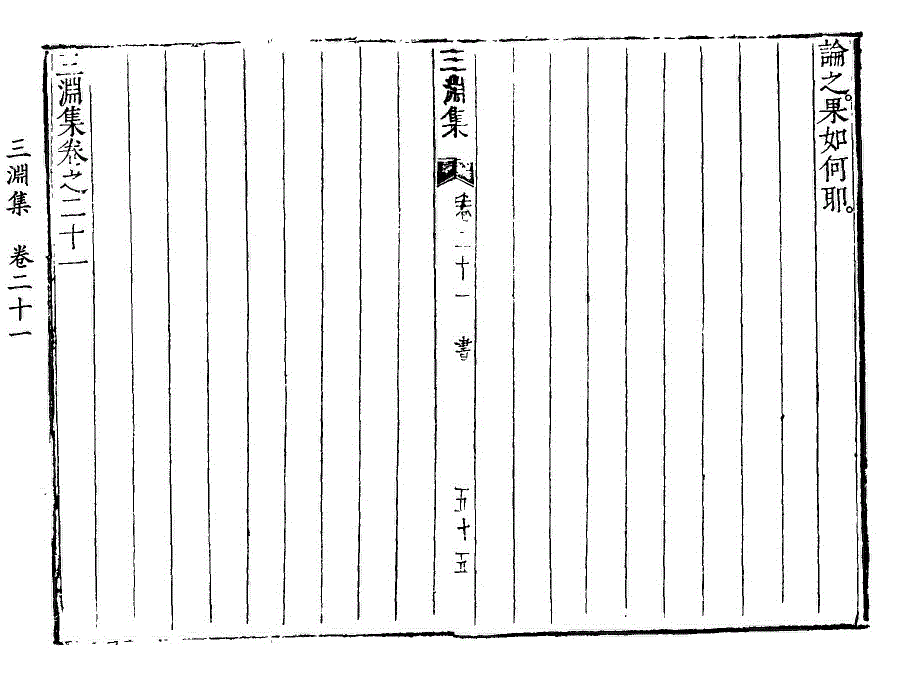 论之。果如何耶。
论之。果如何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