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a 页 WYG1454-070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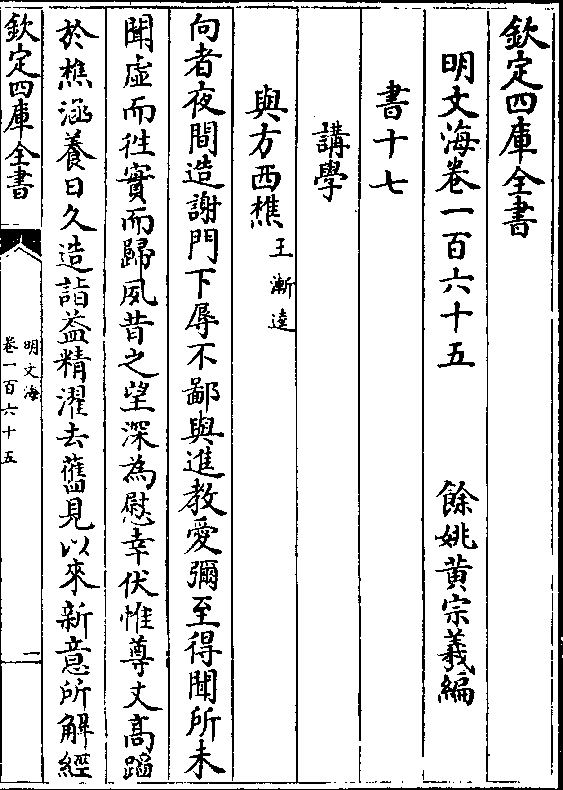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五 馀姚黄宗羲编
书十七
讲学
与方西樵(王渐逵/)
向者夜间造谢门下辱不鄙与进教爱弥至得闻所未
闻虚而往实而归夙昔之望深为慰幸伏惟尊丈高蹈
于樵涵养日久造诣盖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所解经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b 页 WYG1454-070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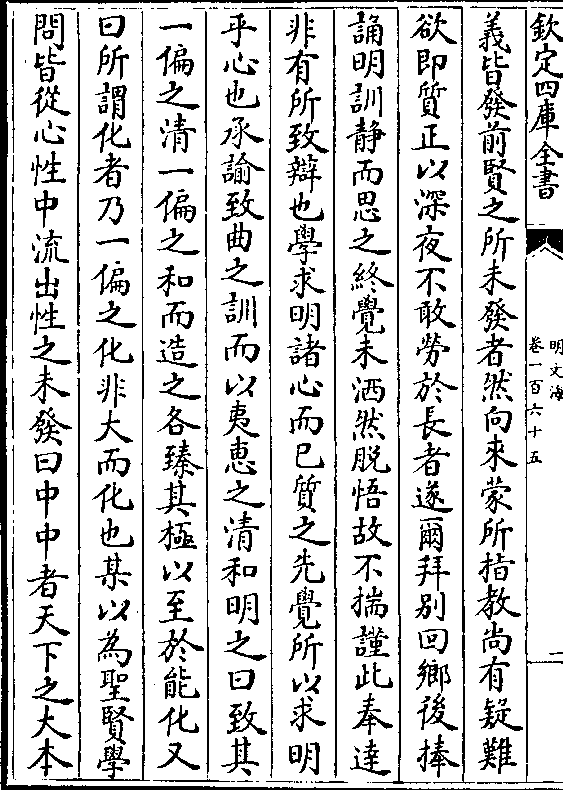 义皆发前贤之所未发者然向来蒙所指教尚有疑难
义皆发前贤之所未发者然向来蒙所指教尚有疑难欲即质正以深夜不敢劳于长者遂尔拜别回乡后捧
诵明训静而思之终觉未洒然脱悟故不揣谨此奉达
非有所致辩也学求明诸心而已质之先觉所以求明
乎心也承谕致曲之训而以夷惠之清和明之曰致其
一偏之清一偏之和而造之各臻其极以至于能化又
曰所谓化者乃一偏之化非大而化也某以为圣贤学
问皆从心性中流出性之未发曰中中者天下之大本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a 页 WYG1454-070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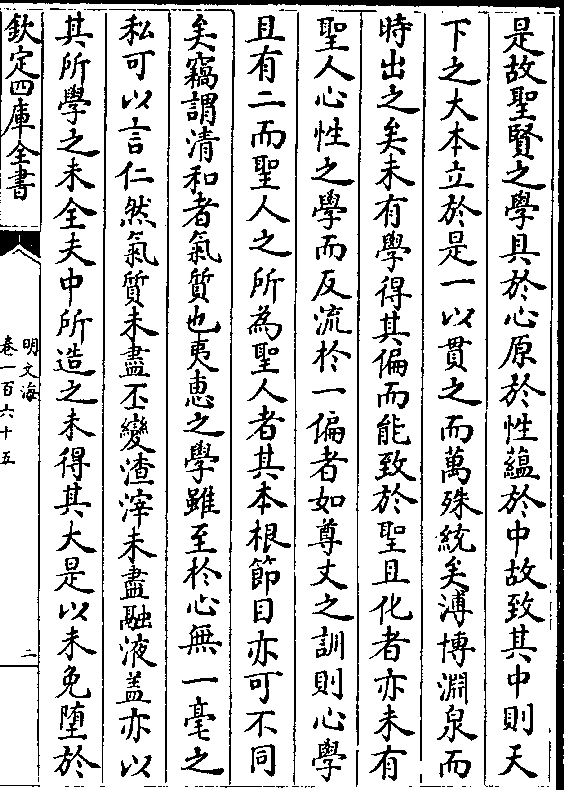 是故圣贤之学具于心原于性蕴于中故致其中则天
是故圣贤之学具于心原于性蕴于中故致其中则天下之大本立于是一以贯之而万殊统矣溥博渊泉而
时出之矣未有学得其偏而能致于圣且化者亦未有
圣人心性之学而反流于一偏者如尊丈之训则心学
且有二而圣人之所为圣人者其本根节目亦可不同
矣窃谓清和者气质也夷惠之学虽至于心无一毫之
私可以言仁然气质未尽丕变渣滓未尽融液盖亦以
其所学之未全夫中所造之未得其大是以未免堕于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b 页 WYG1454-070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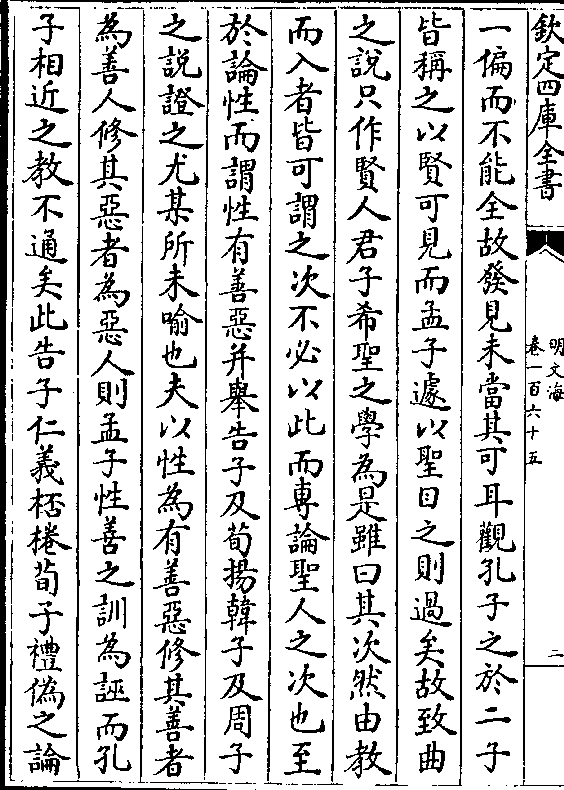 一偏而不能全故发见未当其可耳观孔子之于二子
一偏而不能全故发见未当其可耳观孔子之于二子皆称之以贤可见而孟子遽以圣目之则过矣故致曲
之说只作贤人君子希圣之学为是虽曰其次然由教
而入者皆可谓之次不必以此而专论圣人之次也至
于论性而谓性有善恶并举告子及荀扬韩子及周子
之说證之尤某所未喻也夫以性为有善恶修其善者
为善人修其恶者为恶人则孟子性善之训为诬而孔
子相近之教不通矣此告子仁义杯棬荀子礼伪之论
卷一百六十五 第 3a 页 WYG1454-0709a.png
 之所由起可不必攻也某于宋儒惟取信于明道诸说
之所由起可不必攻也某于宋儒惟取信于明道诸说若以天地气质分之则诚于善恶未能判截反堕于善
恶混之中而与荀扬无异矣明道曰性生道也恻隐之
心人之生道也又曰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此
数言者万世言性之标的也盖某之所谓性者乃一阴
一阳之谓道道之流行曰命命之著物曰性故性者人
物得之以有生即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
谓易故曰人之生道夫人之生也其禀质虽有昏明强
卷一百六十五 第 3b 页 WYG1454-070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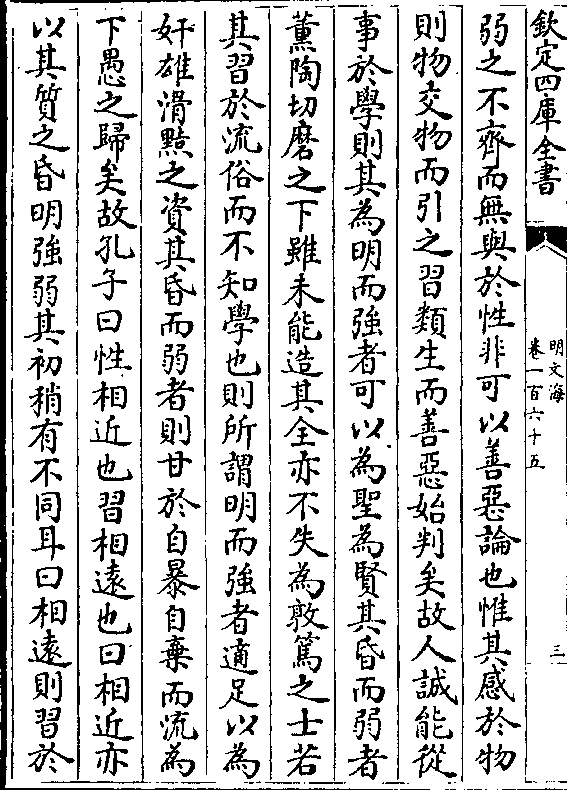 弱之不齐而无与于性非可以善恶论也惟其感于物
弱之不齐而无与于性非可以善恶论也惟其感于物则物交物而引之习类生而善恶始判矣故人诚能从
事于学则其为明而强者可以为圣为贤其昏而弱者
薰陶切磨之下虽未能造其全亦不失为敦笃之士若
其习于流俗而不知学也则所谓明而强者适足以为
奸雄滑黠之资其昏而弱者则甘于自暴自弃而流为
下愚之归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曰相近亦
以其质之昏明强弱其初稍有不同耳曰相远则习于
卷一百六十五 第 4a 页 WYG1454-070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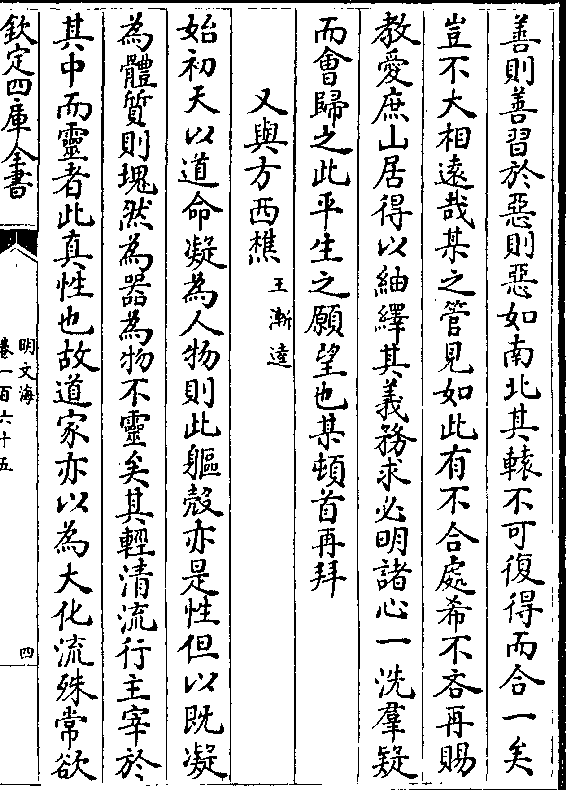 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如南北其辕不可复得而合一矣
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如南北其辕不可复得而合一矣岂不大相远哉某之管见如此有不合处希不吝再赐
教爱庶山居得以䌷绎其义务求必明诸心一洗群疑
而会归之此平生之愿望也某顿首再拜
又与方西樵(王渐逵/)
始初天以道命凝为人物则此躯壳亦是性但以既凝
为体质则块然为器为物不灵矣其轻清流行主宰于
其中而灵者此真性也故道家亦以为大化流殊常欲
卷一百六十五 第 4b 页 WYG1454-070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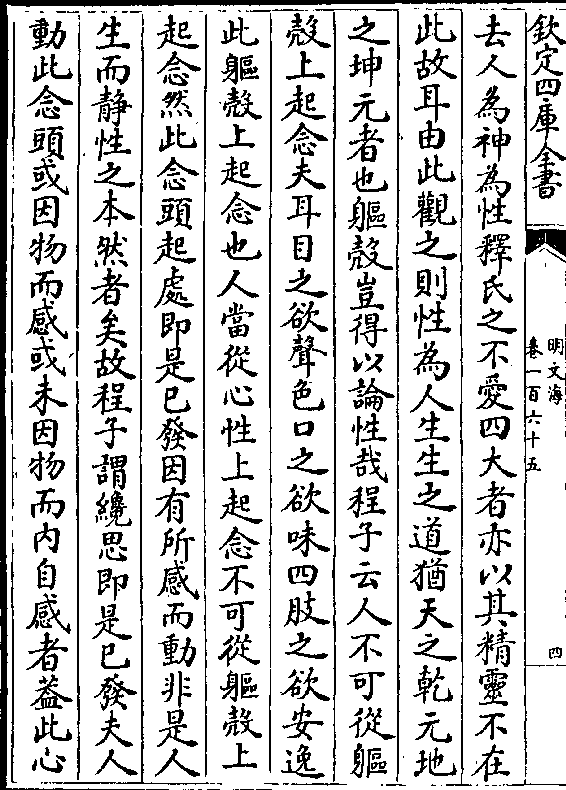 去人为神为性释氏之不爱四大者亦以其精灵不在
去人为神为性释氏之不爱四大者亦以其精灵不在此故耳由此观之则性为人生生之道犹天之乾元地
之坤元者也躯壳岂得以论性哉程子云人不可从躯
壳上起念夫耳目之欲声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
此躯壳上起念也人当从心性上起念不可从躯壳上
起念然此念头起处即是已发因有所感而动非是人
生而静性之本然者矣故程子谓才思即是已发夫人
动此念头或因物而感或未因物而内自感者盖此心
卷一百六十五 第 5a 页 WYG1454-071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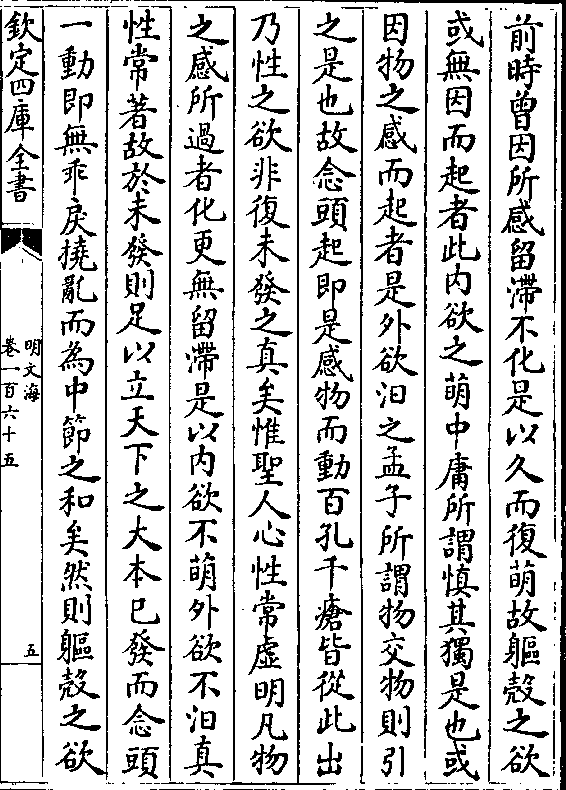 前时曾因所感留滞不化是以久而复萌故躯壳之欲
前时曾因所感留滞不化是以久而复萌故躯壳之欲或无因而起者此内欲之萌中庸所谓慎其独是也或
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汩之孟子所谓物交物则引
之是也故念头起即是感物而动百孔千疮皆从此出
乃性之欲非复未发之真矣惟圣人心性常虚明凡物
之感所过者化更无留滞是以内欲不萌外欲不汩真
性常著故于未发则足以立天下之大本已发而念头
一动即无乖戾挠乱而为中节之和矣然则躯壳之欲
卷一百六十五 第 5b 页 WYG1454-071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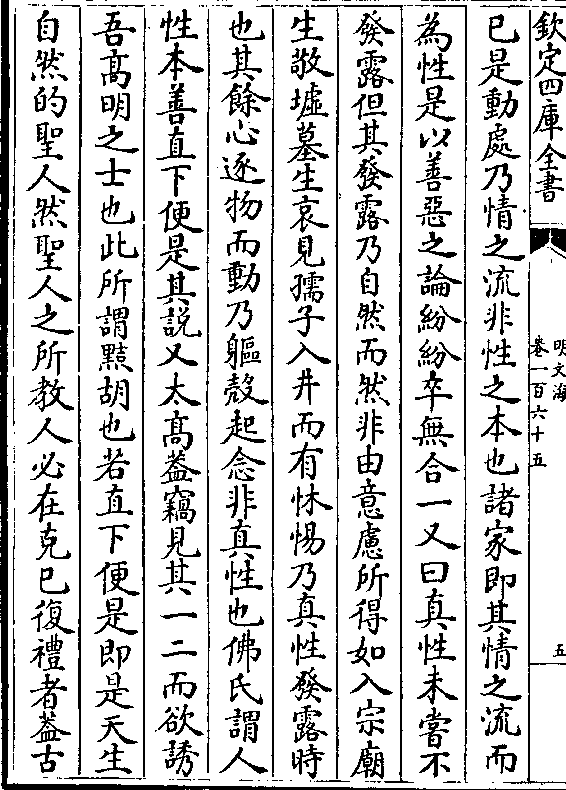 巳是动处乃情之流非性之本也诸家即其情之流而
巳是动处乃情之流非性之本也诸家即其情之流而为性是以善恶之论纷纷卒无合一又曰真性未尝不
发露但其发露乃自然而然非由意虑所得如入宗庙
生敬墟墓生哀见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乃真性发露时
也其馀心逐物而动乃躯壳起念非真性也佛氏谓人
性本善直下便是其说又太高盖窃见其一二而欲诱
吾高明之士也此所谓黠胡也若直下便是即是天生
自然的圣人然圣人之所教人必在克己复礼者盖古
卷一百六十五 第 6a 页 WYG1454-071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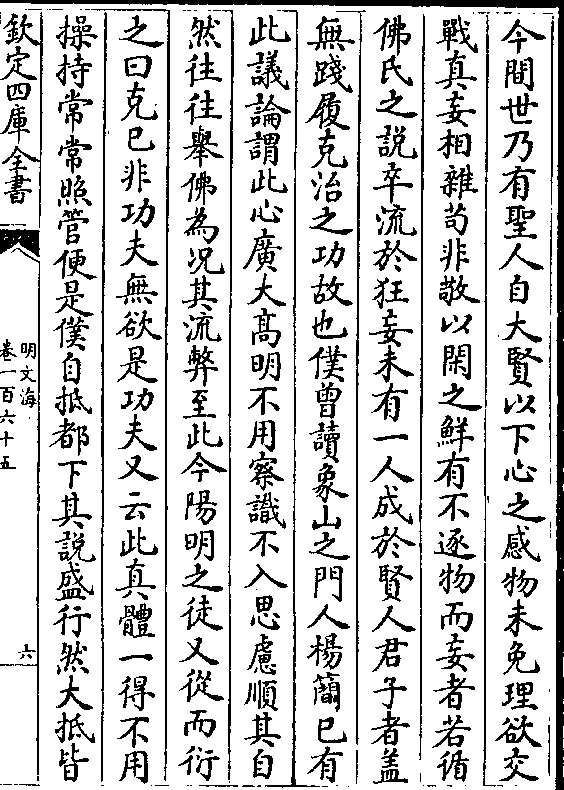 今间世乃有圣人自大贤以下心之感物未免理欲交
今间世乃有圣人自大贤以下心之感物未免理欲交战真妄相杂苟非敬以闲之鲜有不逐物而妄者若循
佛氏之说卒流于狂妄未有一人成于贤人君子者盖
无践履克治之功故也仆曾读象山之门人杨简已有
此议论谓此心广大高明不用察识不入思虑顺其自
然往往举佛为况其流弊至此今阳明之徒又从而衍
之曰克己非功夫无欲是功夫又云此真体一得不用
操持常常照管便是仆自抵都下其说盛行然大抵皆
卷一百六十五 第 6b 页 WYG1454-071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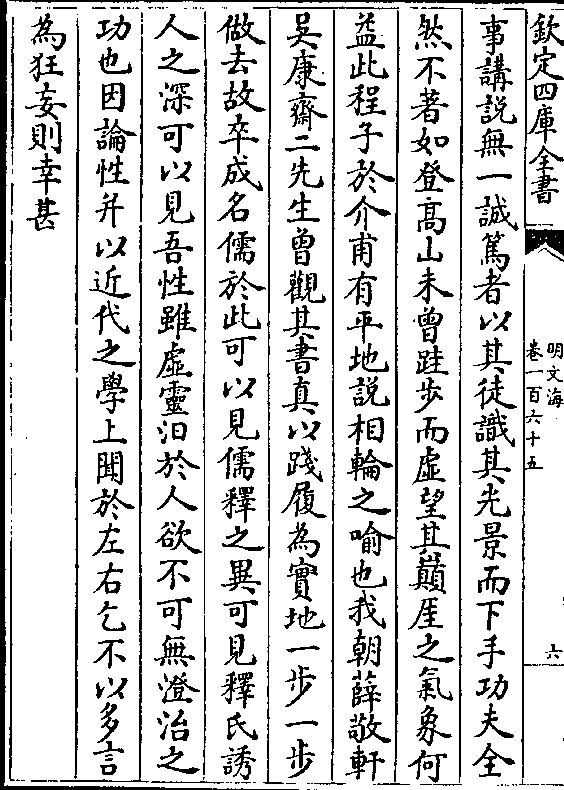 事讲说无一诚笃者以其徒识其光景而下手功夫全
事讲说无一诚笃者以其徒识其光景而下手功夫全然不著如登高山未曾跬步而虚望其巅厓之气象何
益此程子于介甫有平地说相轮之喻也我朝薛敬轩
吴康斋二先生曾观其书真以践履为实地一步一步
做去故卒成名儒于此可以见儒释之异可见释氏诱
人之深可以见吾性虽虚灵汨于人欲不可无澄治之
功也因论性并以近代之学上闻于左右乞不以多言
为狂妄则幸甚
卷一百六十五 第 7a 页 WYG1454-071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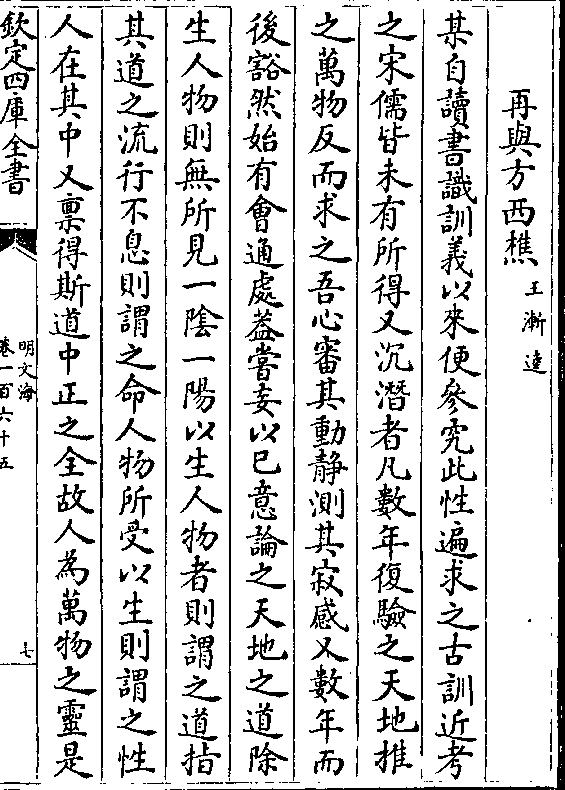 再与方西樵(王渐逵/)
再与方西樵(王渐逵/)某自读书识训义以来便参究此性遍求之古训近考
之宋儒皆未有所得又沉潜者凡数年复验之天地推
之万物反而求之吾心审其动静测其寂感乂数年而
后豁然始有会通处盖尝妄以巳意论之天地之道除
生人物则无所见一阴一阳以生人物者则谓之道指
其道之流行不息则谓之命人物所受以生则谓之性
人在其中乂禀得斯道中正之全故人为万物之灵是
卷一百六十五 第 7b 页 WYG1454-071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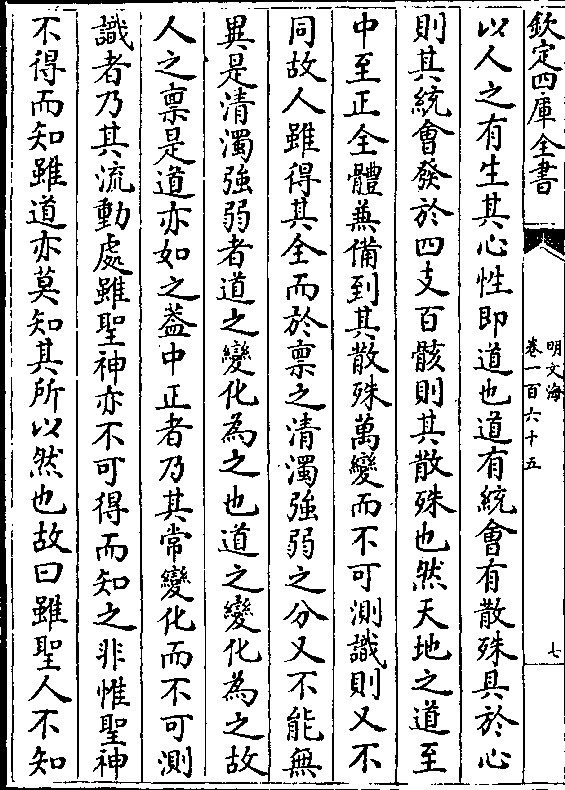 以人之有生其心性即道也道有统会有散殊具于心
以人之有生其心性即道也道有统会有散殊具于心则其统会发于四支百骸则其散殊也然天地之道至
中至正全体兼备到其散殊万变而不可测识则乂不
同故人虽得其全而于禀之清浊强弱之分又不能无
异是清浊强弱者道之变化为之也道之变化为之故
人之禀是道亦如之盖中正者乃其常变化而不可测
识者乃其流动处虽圣神亦不可得而知之非惟圣神
不得而知虽道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故曰虽圣人不知
卷一百六十五 第 8a 页 WYG1454-071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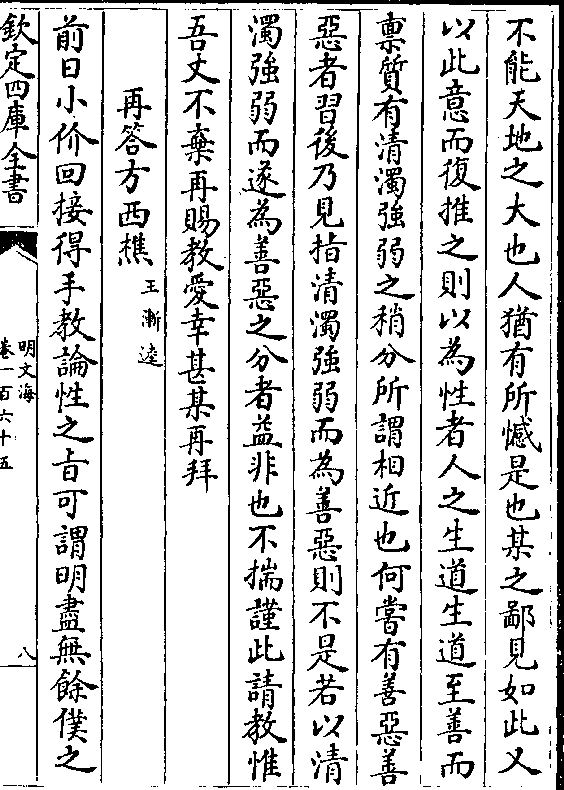 不能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是也某之鄙见如此乂
不能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是也某之鄙见如此乂以此意而复推之则以为性者人之生道生道至善而
禀质有清浊强弱之稍分所谓相近也何尝有善恶善
恶者习后乃见指清浊强弱而为善恶则不是若以清
浊强弱而遂为善恶之分者益非也不揣谨此请教惟
吾丈不弃再赐教爱幸甚某再拜
再答方西樵(王渐逵/)
前日小价回接得手教论性之旨可谓明尽无馀仆之
卷一百六十五 第 8b 页 WYG1454-071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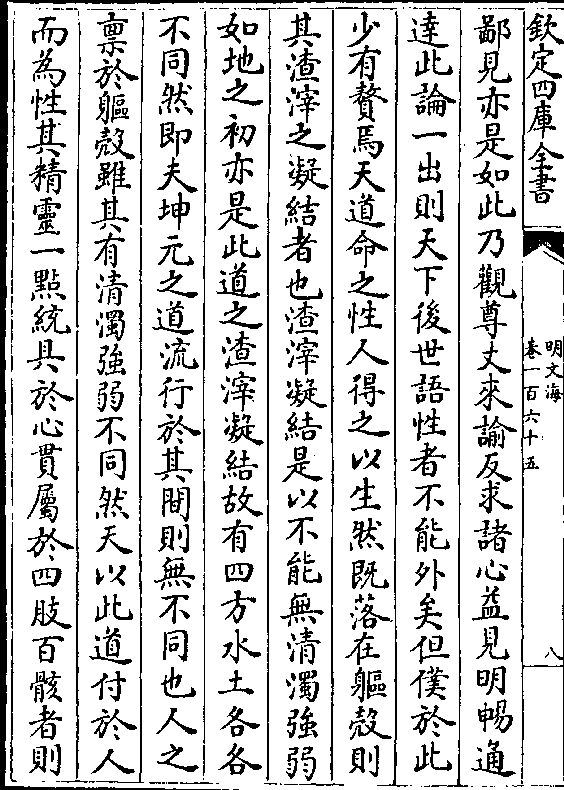 鄙见亦是如此乃观尊丈来谕反求诸心益见明畅通
鄙见亦是如此乃观尊丈来谕反求诸心益见明畅通达此论一出则天下后世语性者不能外矣但仆于此
少有赘焉天道命之性人得之以生然既落在躯壳则
其渣滓之凝结者也渣滓凝结是以不能无清浊强弱
如地之初亦是此道之渣滓凝结故有四方水土各各
不同然即夫坤元之道流行于其间则无不同也人之
禀于躯壳虽其有清浊强弱不同然天以此道付于人
而为性其精灵一点统具于心贯属于四肢百骸者则
卷一百六十五 第 9a 页 WYG1454-071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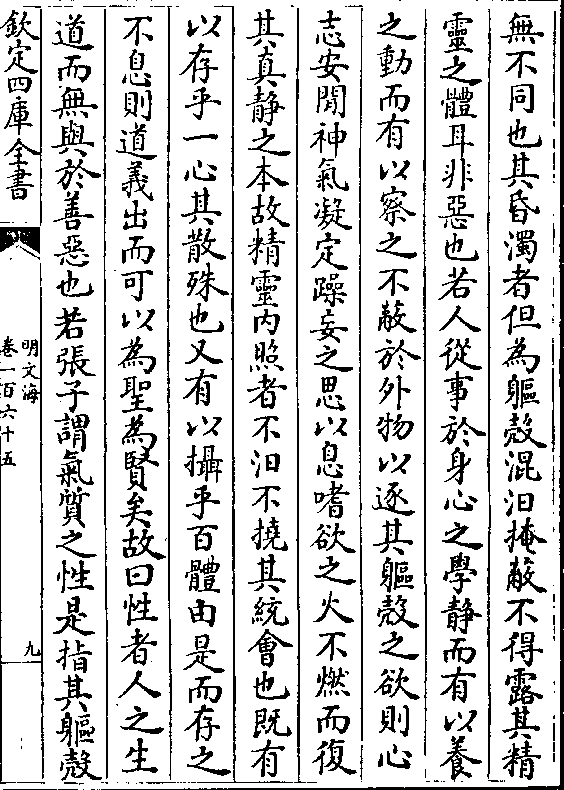 无不同也其昏浊者但为躯壳混汩掩蔽不得露其精
无不同也其昏浊者但为躯壳混汩掩蔽不得露其精灵之体耳非恶也若人从事于身心之学静而有以养
之动而有以察之不蔽于外物以逐其躯壳之欲则心
志安閒神气凝定躁妄之思以息嗜欲之火不燃而复
其真静之本故精灵内照者不汨不挠其统会也既有
以存乎一心其散殊也又有以摄乎百体由是而存之
不息则道义出而可以为圣为贤矣故曰性者人之生
道而无与于善恶也若张子谓气质之性是指其躯壳
卷一百六十五 第 9b 页 WYG1454-071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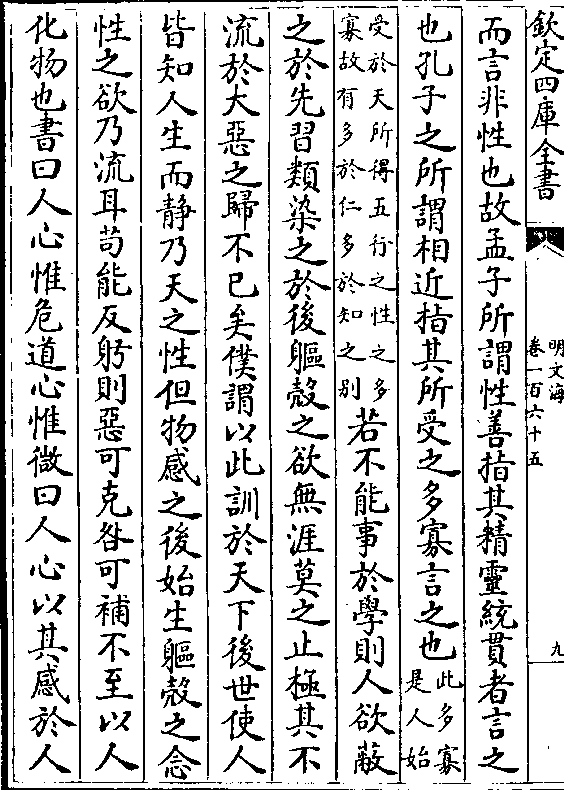 而言非性也故孟子所谓性善指其精灵统贯者言之
而言非性也故孟子所谓性善指其精灵统贯者言之也孔子之所谓相近指其所受之多寡言之也(此多寡/是人始)
(受于天所得五行之性之多/寡故有多于仁多于知之别)若不能事于学则人欲蔽
之于先习类染之于后躯壳之欲无涯莫之止极其不
流于大恶之归不已矣仆谓以此训于天下后世使人
皆知人生而静乃天之性但物感之后始生躯壳之念
性之欲乃流耳苟能反躬则恶可克咎可补不至以人
化物也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人心以其感于人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0a 页 WYG1454-071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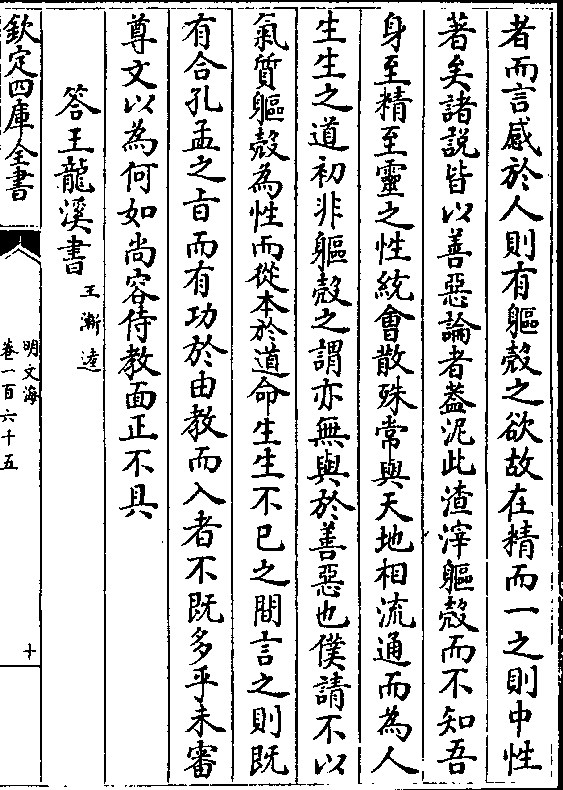 者而言感于人则有躯壳之欲故在精而一之则中性
者而言感于人则有躯壳之欲故在精而一之则中性著矣诸说皆以善恶论者盖泥此渣滓躯壳而不知吾
身至精至灵之性统会散殊常与天地相流通而为人
生生之道初非躯壳之谓亦无与于善恶也仆请不以
气质躯壳为性而从本于道命生生不已之间言之则既
有合孔孟之旨而有功于由教而入者不既多乎未审
尊文以为何如尚容侍教面正不具
答王龙溪书(王渐逵/)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0b 页 WYG1454-0712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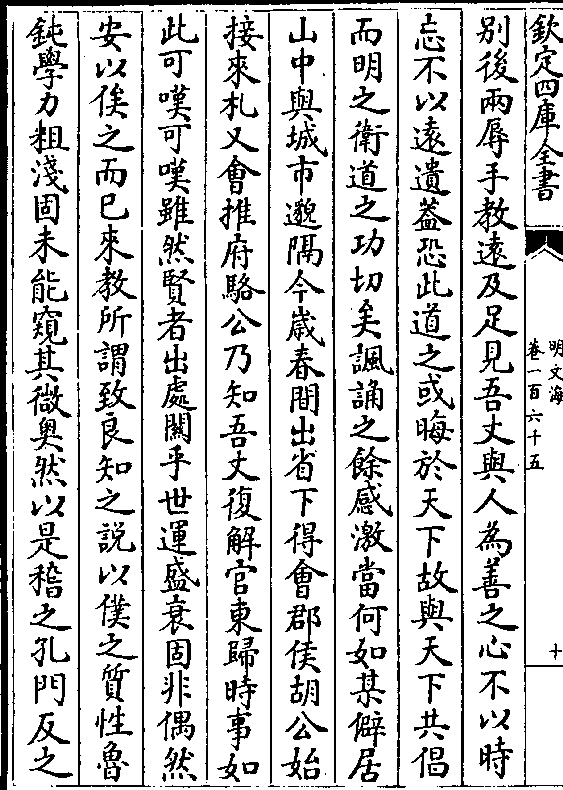 别后两辱手教远及足见吾丈与人为善之心不以时
别后两辱手教远及足见吾丈与人为善之心不以时忘不以远遗盖恐此道之或晦于天下故与天下共倡
而明之卫道之功切矣讽诵之馀感激当何如某僻居
山中与城市邈隔今岁春间出省下得会郡侯胡公始
接来札又会推府骆公乃知吾丈复解官东归时事如
此可叹可叹虽然贤者出处关乎世运盛衰固非偶然
安以俟之而已来教所谓致良知之说以仆之质性鲁
钝学力粗浅固未能窥其微奥然以是稽之孔门反之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1a 页 WYG1454-071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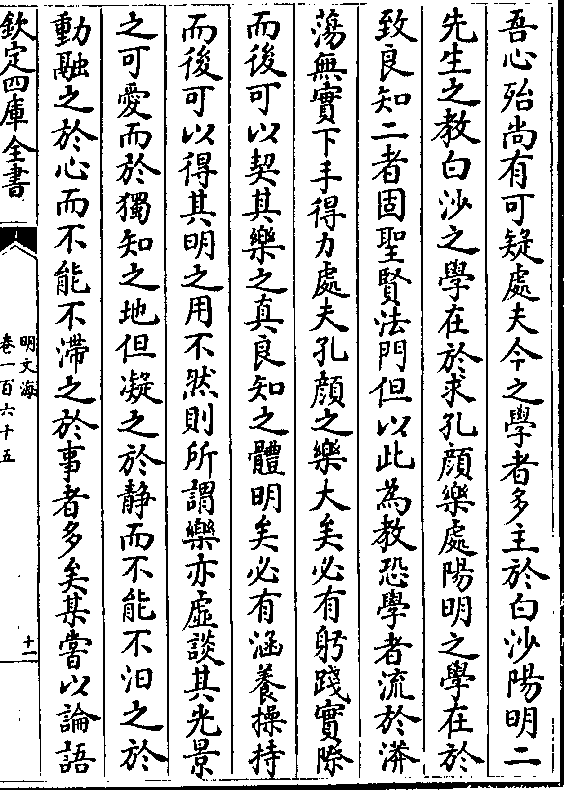 吾心殆尚有可疑处夫今之学者多主于白沙阳明二
吾心殆尚有可疑处夫今之学者多主于白沙阳明二先生之教白沙之学在于求孔颜乐处阳明之学在于
致良知二者固圣贤法门但以此为教恐学者流于漭
荡无实下手得力处夫孔颜之乐大矣必有躬践实际
而后可以契其乐之真良知之体明矣必有涵养操持
而后可以得其明之用不然则所谓乐亦虚谈其光景
之可爱而于独知之地但凝之于静而不能不汨之于
动融之于心而不能不滞之于事者多矣某尝以论语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1b 页 WYG1454-071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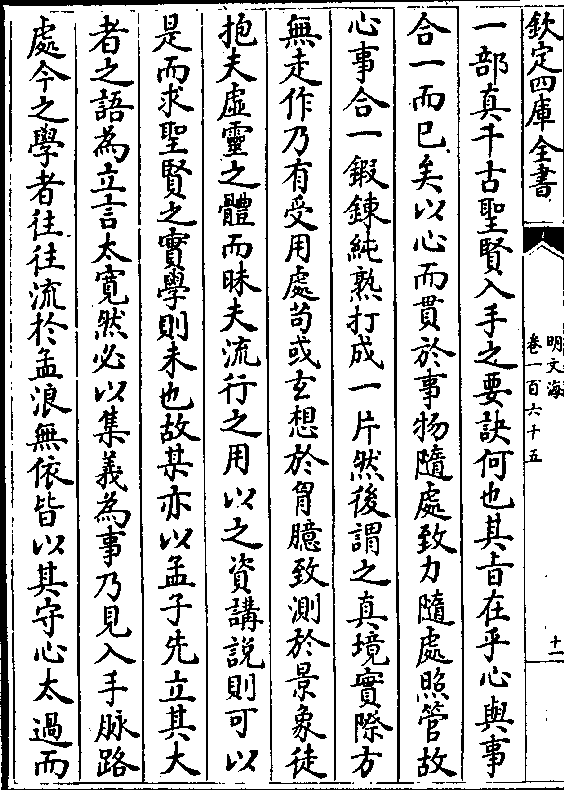 一部真千古圣贤入手之要诀何也其旨在乎心与事
一部真千古圣贤入手之要诀何也其旨在乎心与事合一而已矣以心而贯于事物随处致力随处照管故
心事合一锻鍊纯熟打成一片然后谓之真境实际方
无走作乃有受用处苟或玄想于胸臆致测于景象徒
抱夫虚灵之体而昧夫流行之用以之资讲说则可以
是而求圣贤之实学则未也故某亦以孟子先立其大
者之语为立言太宽然必以集义为事乃见入手脉路
处今之学者往往流于孟浪无依皆以其守心太过而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2a 页 WYG1454-0713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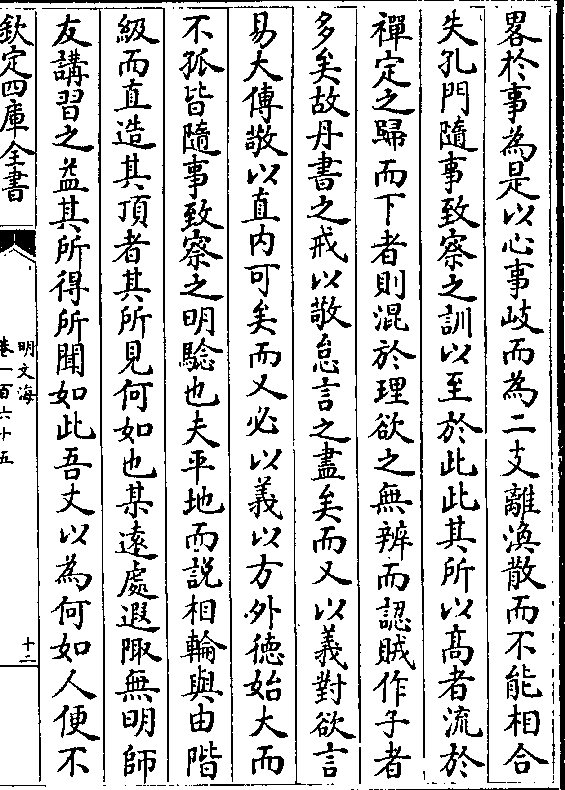 略于事为是以心事岐而为二支离涣散而不能相合
略于事为是以心事岐而为二支离涣散而不能相合失孔门随事致察之训以至于此此其所以高者流于
禅定之归而下者则混于理欲之无辨而认贼作子者
多矣故丹书之戒以敬怠言之尽矣而又以义对欲言
易大传敬以直内可矣而乂必以义以方外德始大而
不孤皆随事致察之明验也夫平地而说相轮与由阶
级而直造其顶者其所见何如也某远处遐陬无明师
友讲习之益其所得所闻如此吾丈以为何如人便不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2b 页 WYG1454-0713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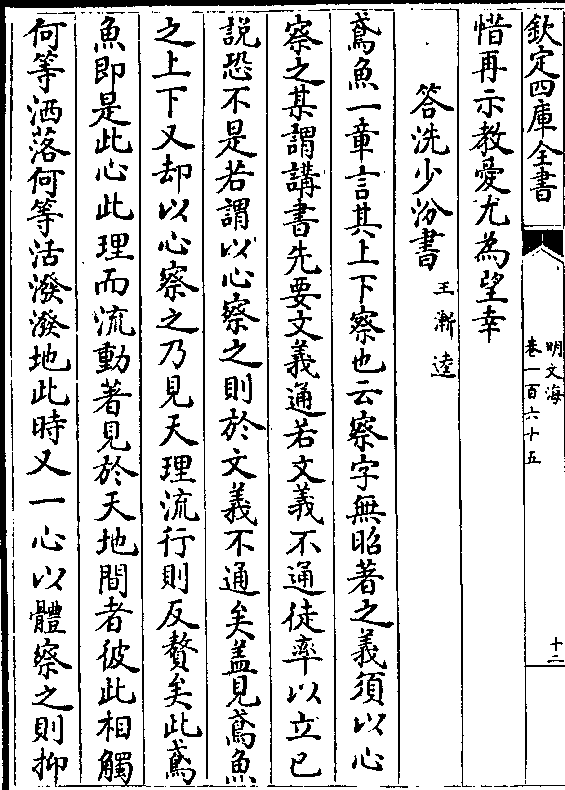 惜再示教爱尤为望幸
惜再示教爱尤为望幸答洗少汾书(王渐逵/)
鸢鱼一章言其上下察也云察字无昭著之义须以心
察之某谓讲书先要文义通若文义不通徒率以立已
说恐不是若谓以心察之则于文义不通矣盖见鸢鱼
之上下又却以心察之乃见天理流行则反赘矣此鸢
鱼即是此心此理而流动著见于天地间者彼此相触
何等洒落何等活泼泼地此时乂一心以体察之则抑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3a 页 WYG1454-0714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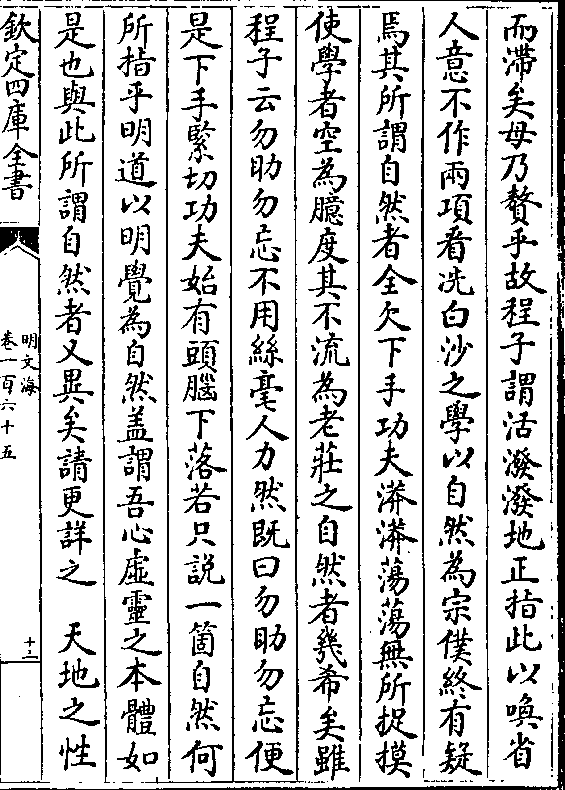 而滞矣母乃赘乎故程子谓活泼泼地正指此以唤省
而滞矣母乃赘乎故程子谓活泼泼地正指此以唤省人意不作两项看冼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仆终有疑
焉其所谓自然者全欠下手功夫漭漭荡荡无所捉摸
使学者空为臆度其不流为老庄之自然者几希矣虽
程子云勿助勿忘不用丝毫人力然既曰勿助勿忘便
是下手𦂳切功夫始有头脑下落若只说一个自然何
所指乎明道以明觉为自然盖谓吾心虚灵之本体如
是也与此所谓自然者又异矣请更详之 天地之性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3b 页 WYG1454-071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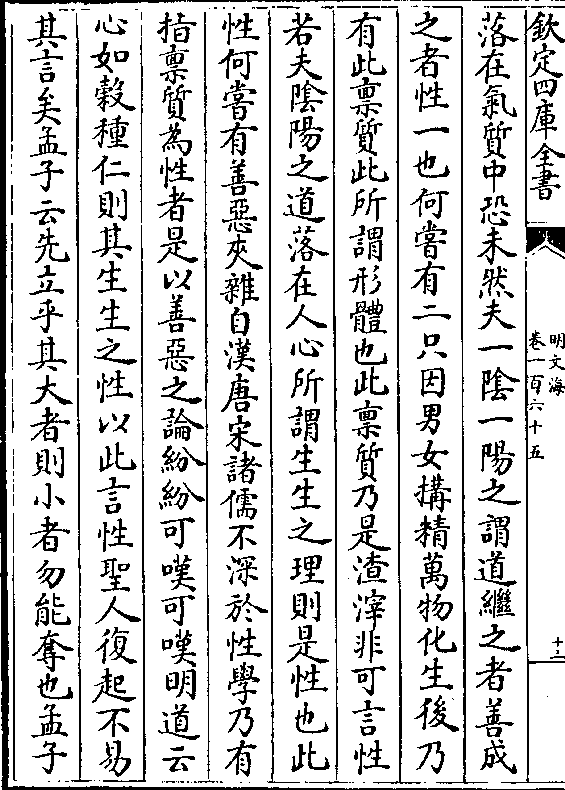 落在气质中恐未然夫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
落在气质中恐未然夫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一也何尝有二只因男女搆精万物化生后乃
有此禀质此所谓形体也此禀质乃是渣滓非可言性
若夫阴阳之道落在人心所谓生生之理则是性也此
性何尝有善恶夹杂自汉唐宋诸儒不深于性学乃有
指禀质为性者是以善恶之论纷纷可叹可叹明道云
心如榖种仁则其生生之性以此言性圣人复起不易
其言矣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勿能夺也孟子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4a 页 WYG1454-0714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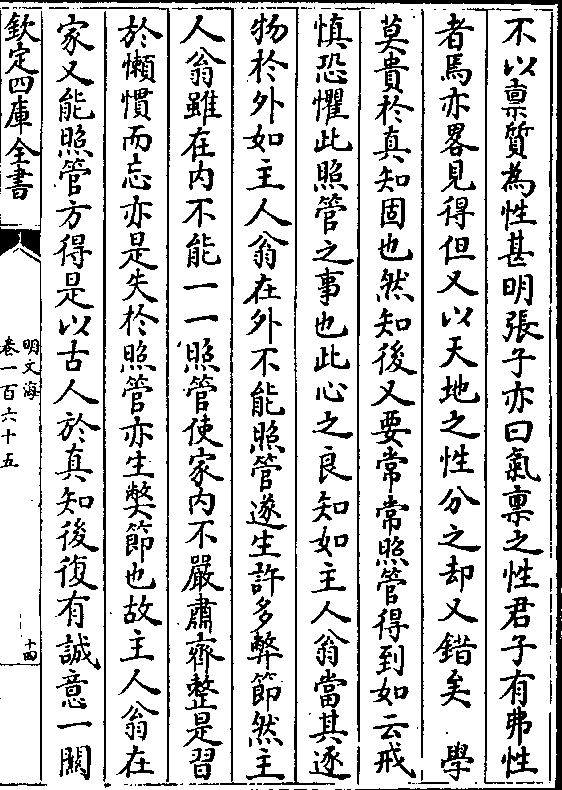 不以禀质为性甚明张子亦曰气禀之性君子有弗性
不以禀质为性甚明张子亦曰气禀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亦略见得但乂以天地之性分之却乂错矣 学
莫贵于真知固也然知后又要常常照管得到如云戒
慎恐惧此照管之事也此心之良知如主人翁当其逐
物于外如主人翁在外不能照管遂生许多弊节然主
人翁虽在内不能一一照管使家内不严肃齐整是习
于懒惯而忘亦是失于照管亦生弊节也故主人翁在
家乂能照管方得是以古人于真知后复有诚意一关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4b 页 WYG1454-071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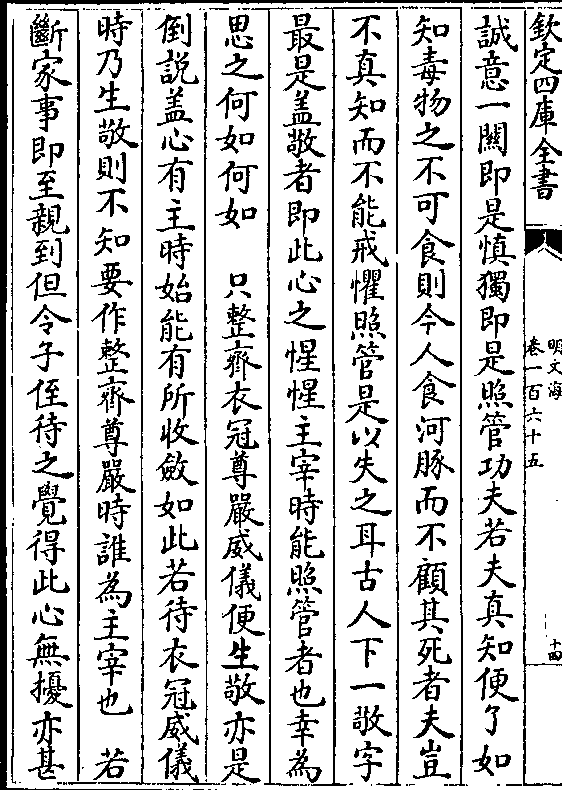 诚意一关即是慎独即是照管功夫若夫真知便了如
诚意一关即是慎独即是照管功夫若夫真知便了如知毒物之不可食则今人食河豚而不顾其死者夫岂
不真知而不能戒惧照管是以失之耳古人下一敬字
最是盖敬者即此心之惺惺主宰时能照管者也幸为
思之何如何如 只整齐衣冠尊严威仪便生敬亦是
倒说盖心有主时始能有所收敛如此若待衣冠威仪
时乃生敬则不知要作整齐尊严时谁为主宰也 若
断家事即至亲到但令子侄待之觉得此心无扰亦甚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5a 页 WYG1454-071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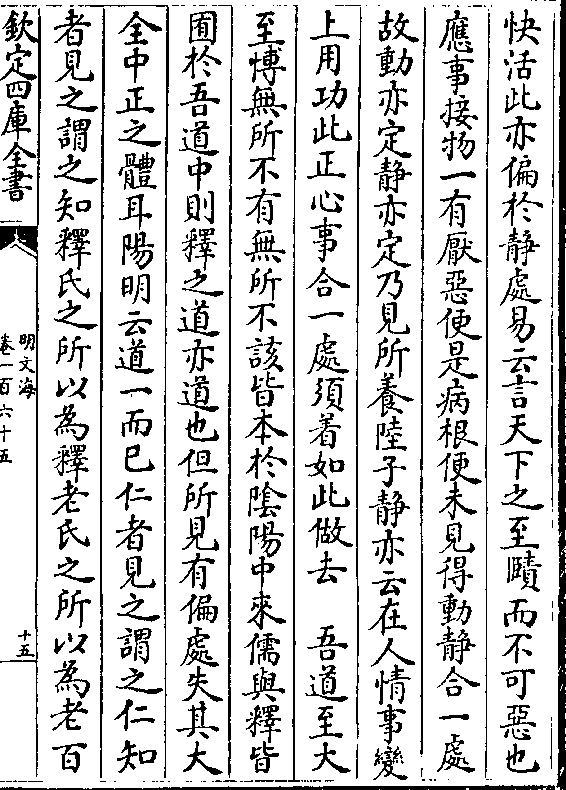 快活此亦偏于静处易云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
快活此亦偏于静处易云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应事接物一有厌恶便是病根便未见得动静合一处
故动亦定静亦定乃见所养陆子静亦云在人情事变
上用功此正心事合一处须着如此做去 吾道至大
至博无所不有无所不该皆本于阴阳中来儒与释皆
囿于吾道中则释之道亦道也但所见有偏处失其大
全中正之体耳阳明云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
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5b 页 WYG1454-071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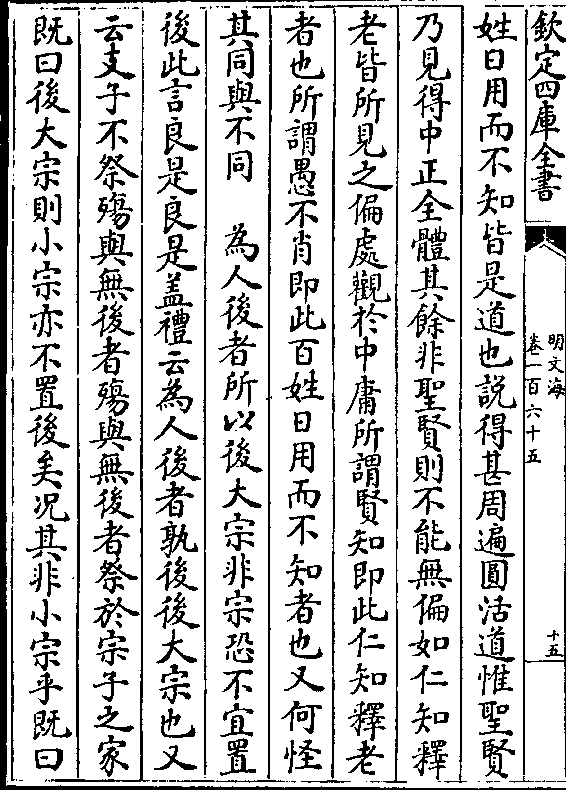 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说得甚周遍圆活道惟圣贤
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说得甚周遍圆活道惟圣贤乃见得中正全体其馀非圣贤则不能无偏如仁知释
老皆所见之偏处观于中庸所谓贤知即此仁知释老
者也所谓愚不肖即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又何怪
其同与不同 为人后者所以后大宗非宗恐不宜置
后此言良是良是盖礼云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乂
云支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
既曰后大宗则小宗亦不置后矣况其非小宗乎既曰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6a 页 WYG1454-071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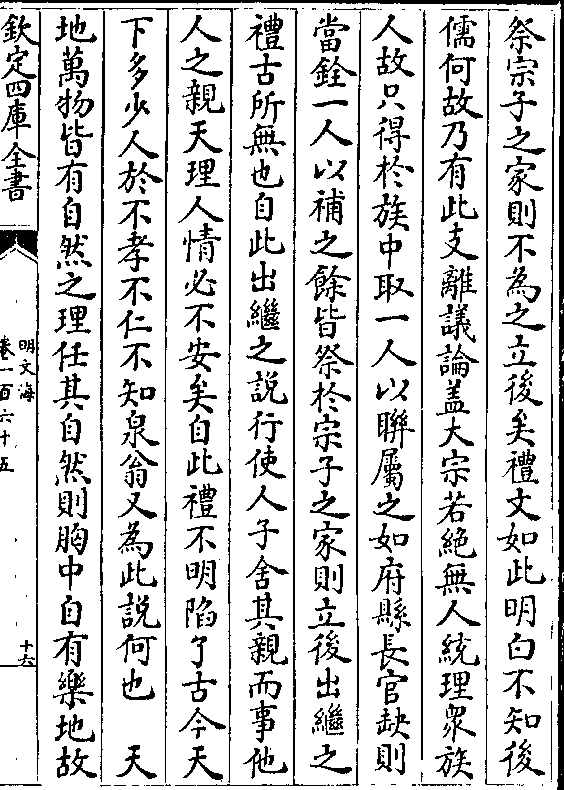 祭宗子之家则不为之立后矣礼文如此明白不知后
祭宗子之家则不为之立后矣礼文如此明白不知后儒何故乃有此支离议论盖大宗若绝无人统理众族
人故只得于族中取一人以联属之如府县长官缺则
当铨一人以补之馀皆祭于宗子之家则立后出继之
礼古所无也自此出继之说行使人子舍其亲而事他
人之亲天理人情必不安矣自此礼不明陷了古今天
下多少人于不孝不仁不知泉翁又为此说何也 天
地万物皆有自然之理任其自然则胸中自有乐地故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6b 页 WYG1454-0715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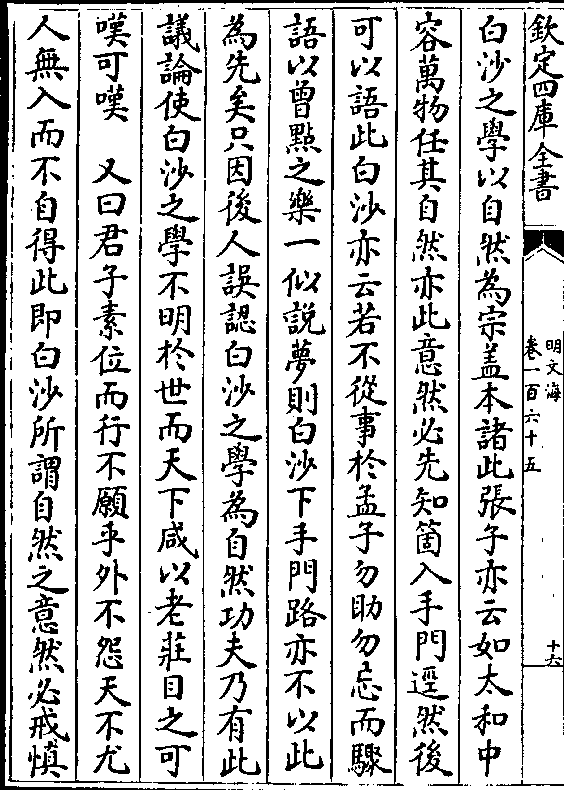 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盖本诸此张子亦云如太和中
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盖本诸此张子亦云如太和中容万物任其自然亦此意然必先知个入手门径然后
可以语此白沙亦云若不从事于孟子勿助勿忘而骤
语以曾点之乐一似说梦则白沙下手门路亦不以此
为先矣只因后人误认白沙之学为自然功夫乃有此
议论使白沙之学不明于世而天下咸以老庄目之可
叹可叹 又曰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不怨天不尤
人无入而不自得此即白沙所谓自然之意然必戒慎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7a 页 WYG1454-0716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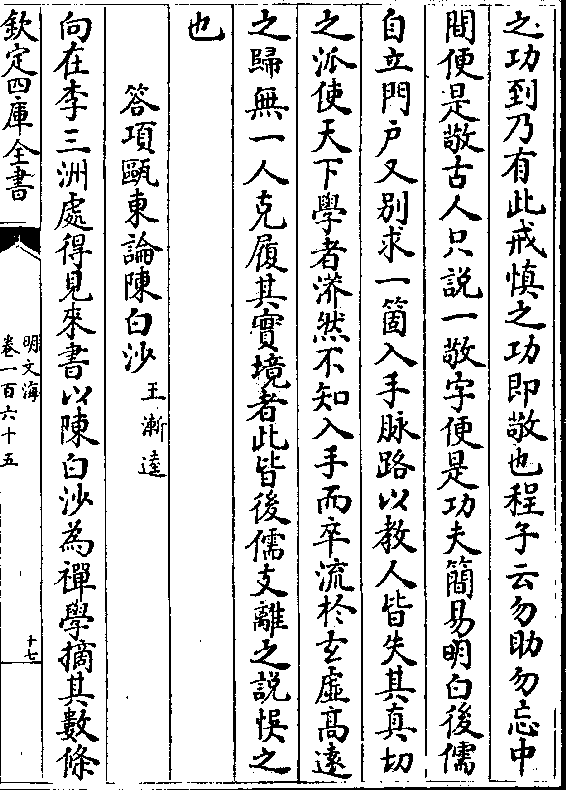 之功到乃有此戒慎之功即敬也程子云勿助勿忘中
之功到乃有此戒慎之功即敬也程子云勿助勿忘中间便是敬古人只说一敬字便是功夫简易明白后儒
自立门户又别求一个入手脉路以教人皆失其真切
之𣲖使天下学者漭然不知入手而卒流于玄虚高远
之归无一人克履其实境者此皆后儒支离之说误之
也
答项瓯东论陈白沙(王渐逵/)
向在李三洲处得见来书以陈白沙为禅学摘其数条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7b 页 WYG1454-071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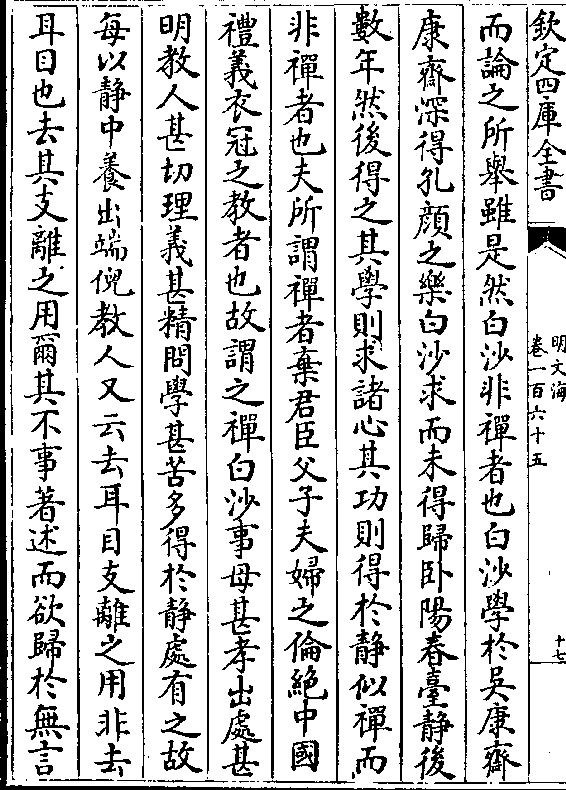 而论之所举虽是然白沙非禅者也白沙学于吴康斋
而论之所举虽是然白沙非禅者也白沙学于吴康斋康斋深得孔颜之乐白沙求而未得归卧阳春台静后
数年然后得之其学则求诸心其功则得于静似禅而
非禅者也夫所谓禅者弃君臣父子夫妇之伦绝中国
礼义衣冠之教者也故谓之禅白沙事母甚孝出处甚
明教人甚切理义甚精问学甚苦多得于静处有之故
每以静中养出端倪教人又云去耳目支离之用非去
耳目也去其支离之用尔其不事著述而欲归于无言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8a 页 WYG1454-071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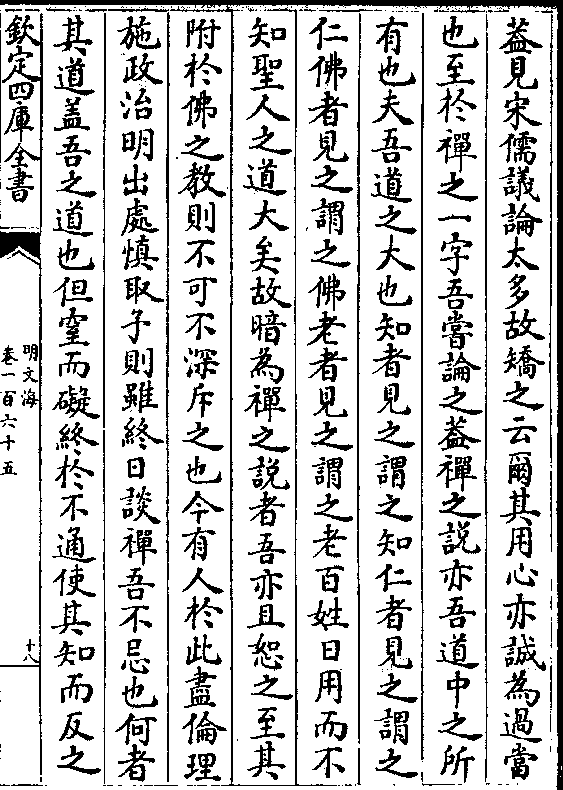 盖见宋儒议论太多故矫之云尔其用心亦诚为过当
盖见宋儒议论太多故矫之云尔其用心亦诚为过当也至于禅之一字吾尝论之盖禅之说亦吾道中之所
有也夫吾道之大也知者见之谓之知仁者见之谓之
仁佛者见之谓之佛老者见之谓之老百姓日用而不
知圣人之道大矣故暗为禅之说者吾亦且恕之至其
附于佛之教则不可不深斥之也今有人于此尽伦理
施政治明出处慎取予则虽终日谈禅吾不忌也何者
其道盖吾之道也但窒而碍终于不通使其知而反之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8b 页 WYG1454-071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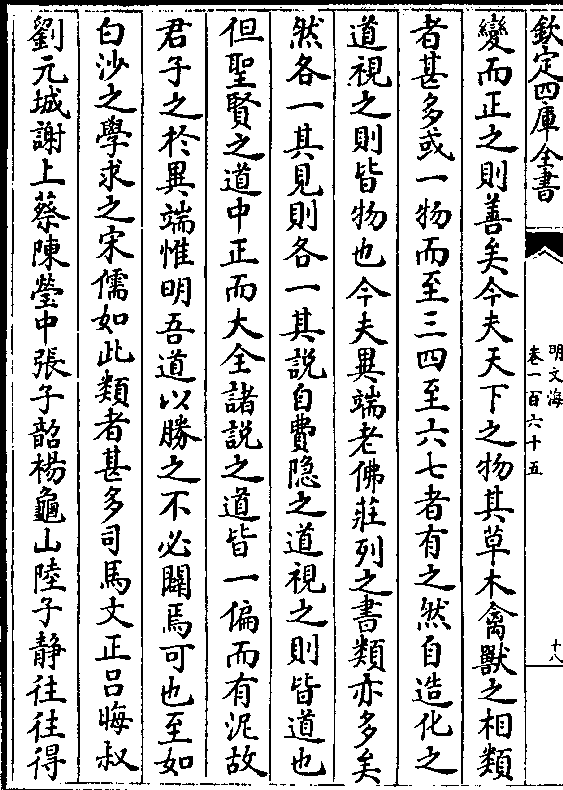 变而正之则善矣今夫天下之物其草木禽兽之相类
变而正之则善矣今夫天下之物其草木禽兽之相类者甚多或一物而至三四至六七者有之然自造化之
道视之则皆物也今夫异端老佛庄列之书类亦多矣
然各一其见则各一其说自费隐之道视之则皆道也
但圣贤之道中正而大全诸说之道皆一偏而有泥故
君子之于异端惟明吾道以胜之不必辟焉可也至如
白沙之学求之宋儒如此类者甚多司马文正吕晦叔
刘元城谢上蔡陈莹中张子韶杨龟山陆子静往往得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9a 页 WYG1454-0717a.png
 于禅学改头换面处有之然于身心国家皆无愧歉天
于禅学改头换面处有之然于身心国家皆无愧歉天下后世皆尊仰之此禅学之变正而非禅矣何可怪乎
白沙之学多著于静固有偏处而其本根节目则同岂
谓之禅乎虽然禅而归于正则可恕禅而附于佛谓佛
为西方圣人欲阴附其教则有大害于中国宜在所痛
斥而不少假借焉可也盖佛者西域之人其法西域之
法是故西域之法毁纲常灭人道遏化生之机伤天地
之和其风声气习一入于中国中国受之则生变乱如
卷一百六十五 第 19b 页 WYG1454-071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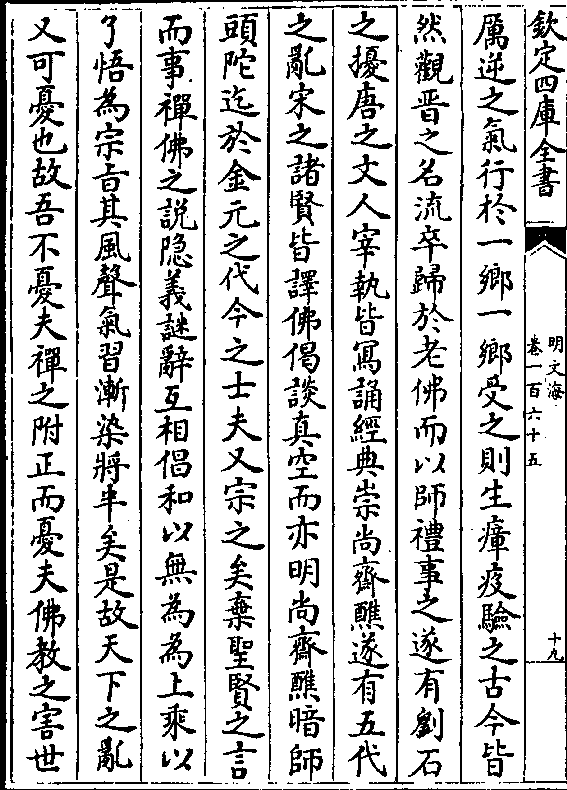 厉逆之气行于一乡一乡受之则生瘴疫验之古今皆
厉逆之气行于一乡一乡受之则生瘴疫验之古今皆然观晋之名流卒归于老佛而以师礼事之遂有刘石
之扰唐之文人宰执皆写诵经典崇尚斋醮遂有五代
之乱宋之诸贤皆译佛偈谈真空而亦明尚斋醮暗师
头陀迄于金元之代今之士夫乂宗之矣弃圣贤之言
而事禅佛之说隐义谜辞互相倡和以无为为上乘以
了悟为宗旨其风声气习渐染将半矣是故天下之乱
又可忧也故吾不忧夫禅之附正而忧夫佛教之害世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0a 页 WYG1454-071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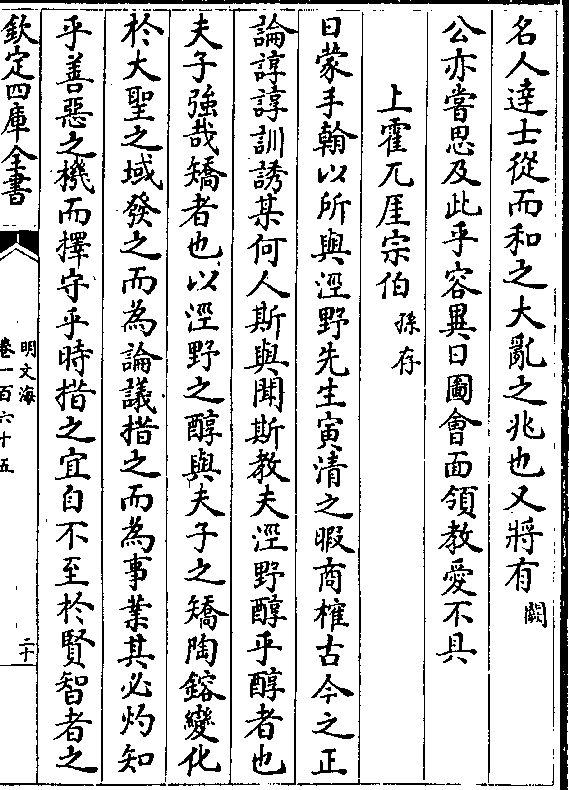 名人达士从而和之大乱之兆也又将有(阙/)
名人达士从而和之大乱之兆也又将有(阙/)公亦尝思及此乎容异日图会面领教爱不具
上霍兀厓宗伯(孙存/)
日蒙手翰以所与泾野先生寅清之暇商𣙜古今之正
论谆谆训诱某何人斯与闻斯教夫泾野醇乎醇者也
夫子强哉矫者也以泾野之醇与夫子之矫陶镕变化
于大圣之域发之而为论议措之而为事业其必灼知
乎善恶之机而择守乎时措之宜自不至于贤智者之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0b 页 WYG1454-071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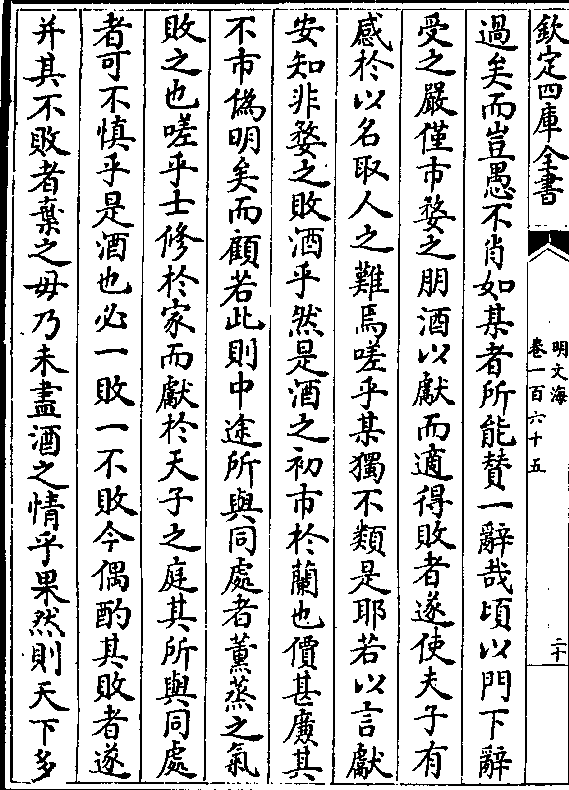 过矣而岂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赞一辞哉顷以门下辞
过矣而岂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赞一辞哉顷以门下辞受之严仅市婺之朋酒以献而适得败者遂使夫子有
感于以名取人之难焉嗟乎某独不类是耶若以言献
安知非婺之败酒乎然是酒之初市于兰也价甚廉其
不市伪明矣而顾若此则中途所与同处者薰蒸之气
败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献于天子之庭其所与同处
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败一不败今偶酌其败者遂
并其不败者弃之毋乃未尽酒之情乎果然则天下多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1a 页 WYG1454-071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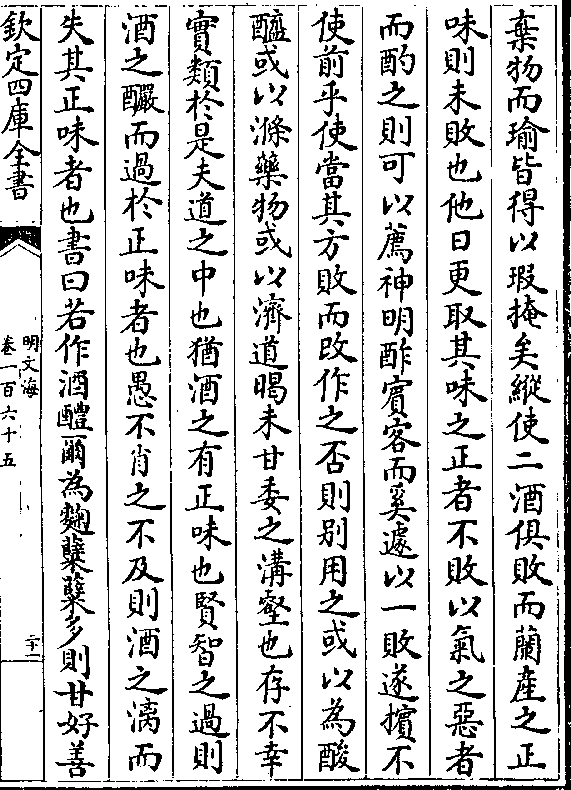 弃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纵使二酒俱败而兰产之正
弃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纵使二酒俱败而兰产之正味则未败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败以气之恶者
而酌之则可以荐神明酢宾客而奚遽以一败遂摈不
使前乎使当其方败而改作之否则别用之或以为酸
醯或以涤药物或以济道暍未甘委之沟壑也存不幸
实类于是夫道之中也犹酒之有正味也贤智之过则
酒之酽而过于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则酒之漓而
失其正味者也书曰若作酒醴尔为曲糵糵多则甘好善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1b 页 WYG1454-071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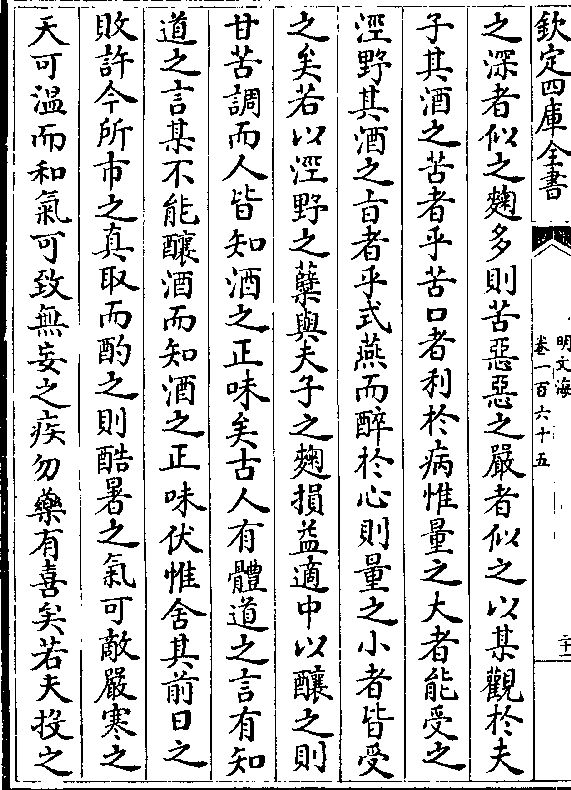 之深者似之曲多则苦恶恶之严者似之以某观于夫
之深者似之曲多则苦恶恶之严者似之以某观于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于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
泾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于心则量之小者皆受
之矣若以泾野之糵与夫子之曲损益适中以酿之则
甘苦调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体道之言有知
道之言某不能酿酒而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
败许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则酷暑之气可敌严寒之
天可温而和气可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矣若夫投之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2a 页 WYG1454-071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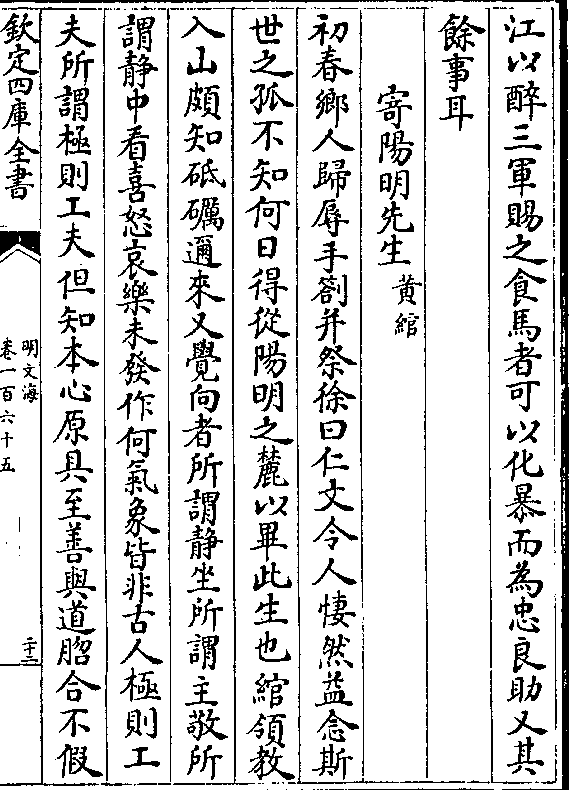 江以醉三军赐之食马者可以化暴而为忠良助又其
江以醉三军赐之食马者可以化暴而为忠良助又其馀事耳
寄阳明先生(黄绾/)
初春乡人归辱手劄并祭徐曰仁文令人悽然益念斯
世之孤不知何日得从阳明之麓以毕此生也绾领教
入山颇知砥砺迩来乂觉向者所谓静坐所谓主敬所
谓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作何气象皆非古人极则工
夫所谓极则工夫但知本心原具至善与道吻合不假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2b 页 WYG1454-071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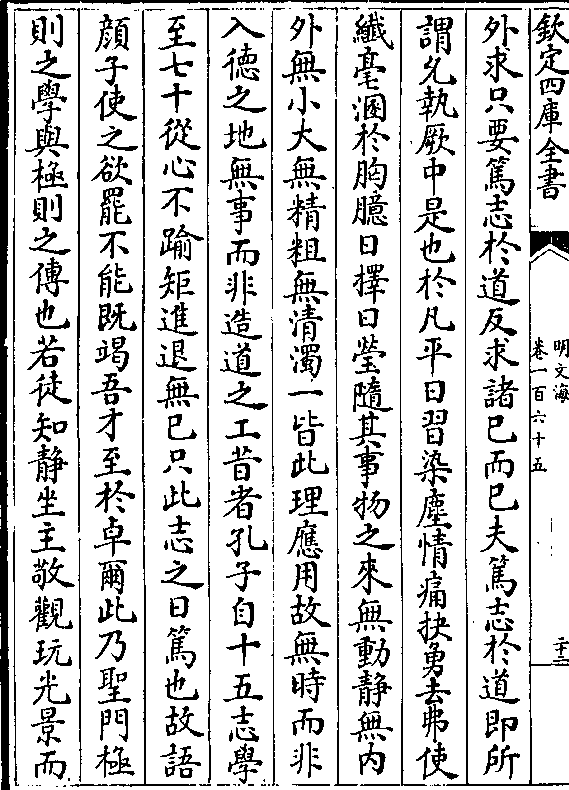 外求只要笃志于道反求诸已而已夫笃志于道即所
外求只要笃志于道反求诸已而已夫笃志于道即所谓允执厥中是也于凡平日习染尘情痛抉勇去弗使
纤毫溷于胸臆日择日莹随其事物之来无动静无内
外无小大无精粗无清浊一皆此理应用故无时而非
入德之地无事而非造道之工昔者孔子自十五志学
至七十从心不踰矩进退无已只此志之日笃也故语
颜子使之欲罢不能既竭吾才至于卓尔此乃圣门极
则之学与极则之传也若徒知静坐主敬观玩光景而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3a 页 WYG1454-0719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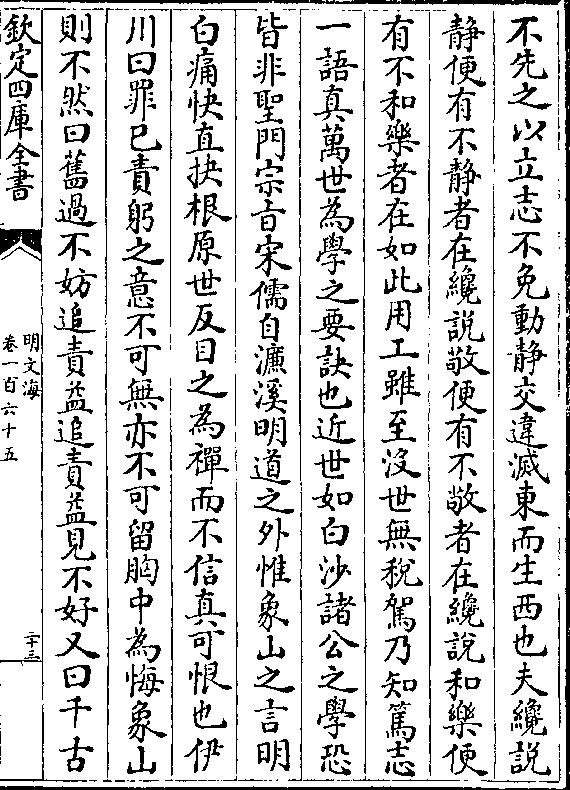 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动静交违灭东而生西也夫才说
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动静交违灭东而生西也夫才说静便有不静者在才说敬便有不敬者在才说和乐便
有不和乐者在如此用工虽至没世无税驾乃知笃志
一语真万世为学之要诀也近世如白沙诸公之学恐
皆非圣门宗旨宋儒自濂溪明道之外惟象山之言明
白痛快直抉根原世反目之为禅而不信真可恨也伊
川曰罪己责躬之意不可无亦不可留胸中为悔象山
则不然曰旧过不妨追责益追责益见不好又曰千古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3b 页 WYG1454-071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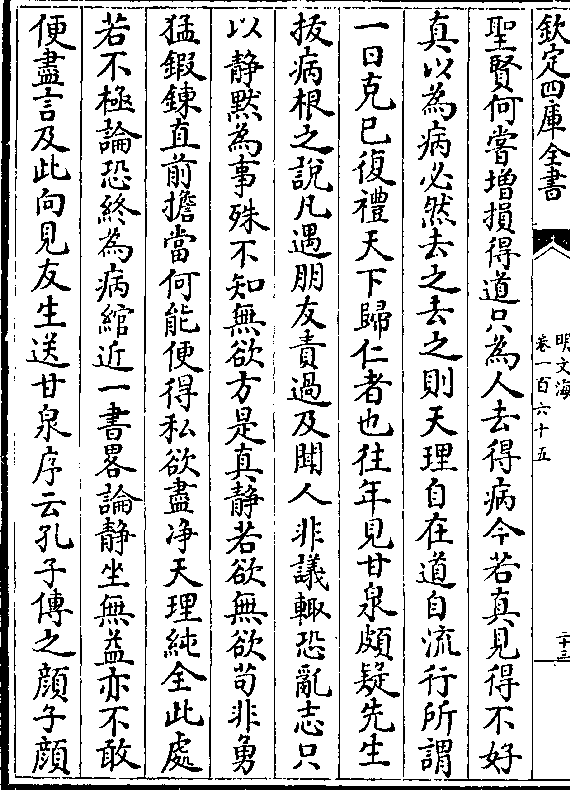 圣贤何尝增损得道只为人去得病今若真见得不好
圣贤何尝增损得道只为人去得病今若真见得不好真以为病必然去之去之则天理自在道自流行所谓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者也往年见甘泉颇疑先生
拔病根之说凡遇朋友责过及闻人非议辄恐乱志只
以静默为事殊不知无欲方是真静若欲无欲苟非勇
猛锻鍊直前担当何能便得私欲尽净天理纯全此处
若不极论恐终为病绾近一书略论静坐无益亦不敢
便尽言及此向见友生送甘泉序云孔子传之颜子颜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4a 页 WYG1454-071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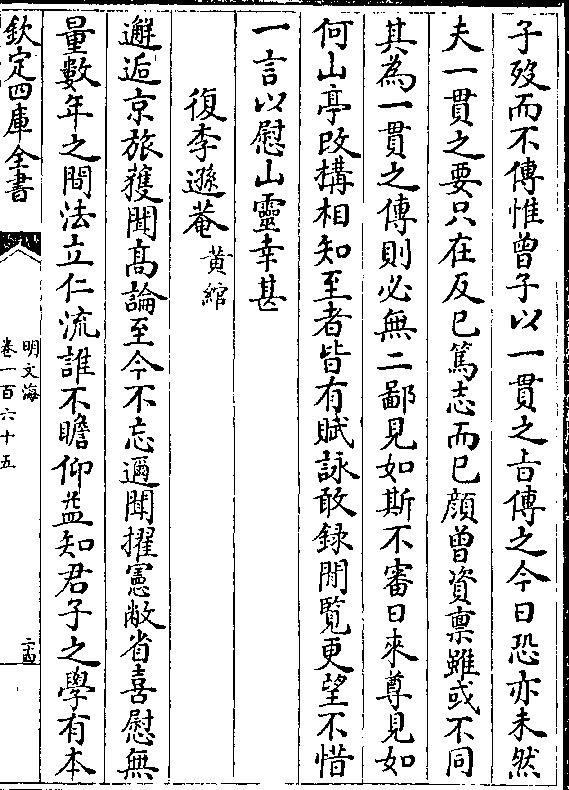 子殁而不传惟曾子以一贯之旨传之今日恐亦未然
子殁而不传惟曾子以一贯之旨传之今日恐亦未然夫一贯之要只在反已笃志而已颜曾资禀虽或不同
其为一贯之传则必无二鄙见如斯不审日来尊见如
何山亭改搆相知至者皆有赋咏敢录閒览更望不惜
一言以慰山灵幸甚
复李逊庵(黄绾/)
邂逅京旅获闻高论至今不忘迩闻擢宪敝省喜慰无
量数年之间法立仁流谁不瞻仰益知君子之学有本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4b 页 WYG1454-071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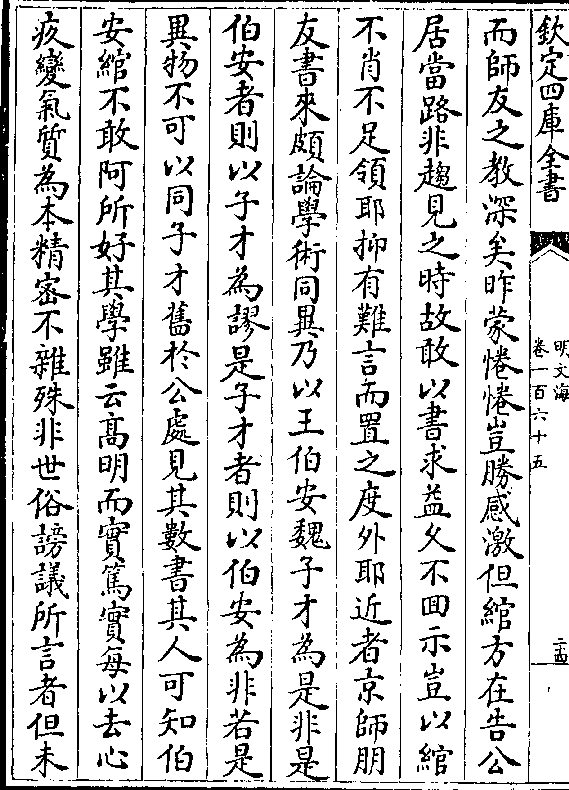 而师友之教深矣昨蒙惓惓岂胜感激但绾方在告公
而师友之教深矣昨蒙惓惓岂胜感激但绾方在告公居当路非趋见之时故敢以书求益久不回示岂以绾
不肖不足领耶抑有难言而置之度外耶近者京师朋
友书来颇论学术同异乃以王伯安魏子才为是非是
伯安者则以子才为谬是子才者则以伯安为非若是
异物不可以同子才旧于公处见其数书其人可知伯
安绾不敢阿所好其学虽云高明而实笃实每以去心
疚变气质为本精密不杂殊非世俗谤议所言者但未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5a 页 WYG1454-072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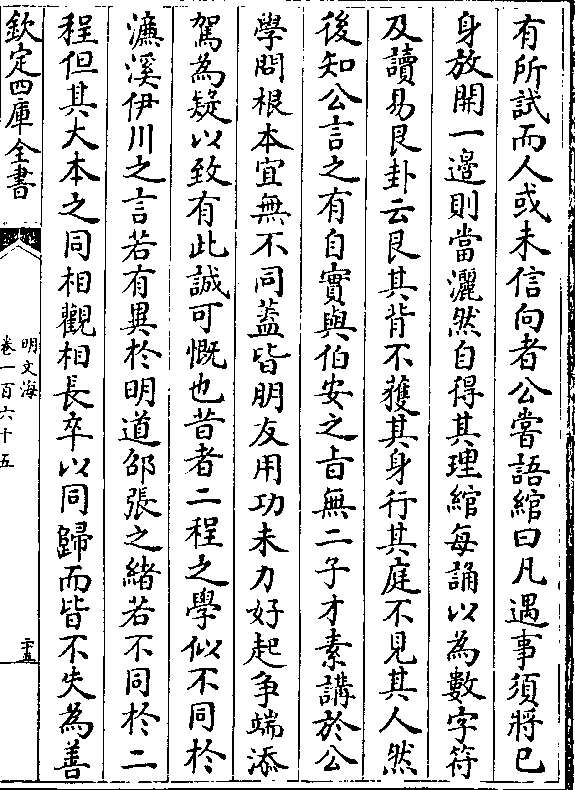 有所试而人或未信向者公尝语绾曰凡遇事须将已
有所试而人或未信向者公尝语绾曰凡遇事须将已身放开一边则当洒然自得其理绾每诵以为数字符
及读易艮卦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然
后知公言之有自实与伯安之旨无二子才素讲于公
学问根本宜无不同盖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争端添
驾为疑以致有此诚可慨也昔者二程之学似不同于
濂溪伊川之言若有异于明道邵张之绪若不同于二
程但其大本之同相观相长卒以同归而皆不失为善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5b 页 WYG1454-072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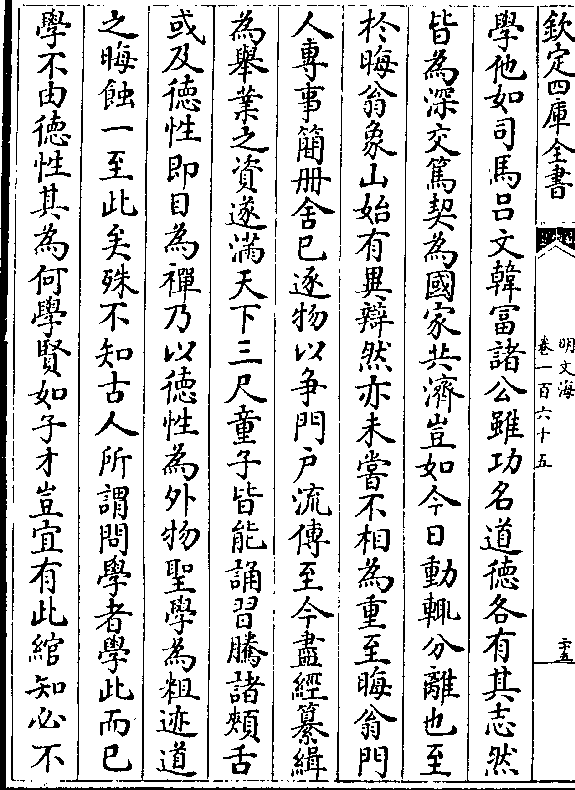 学他如司马吕文韩富诸公虽功名道德各有其志然
学他如司马吕文韩富诸公虽功名道德各有其志然皆为深交笃契为国家共济岂如今日动辄分离也至
于晦翁象山始有异辩然亦未尝不相为重至晦翁门
人专事简册舍巳逐物以争门户流传至今尽经纂缉
为举业之资遂满天下三尺童子皆能诵习腾诸颊舌
或及德性即目为禅乃以德性为外物圣学为粗迹道
之晦蚀一至此矣殊不知古人所谓问学者学此而已
学不由德性其为何学贤如子才岂宜有此绾知必不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6a 页 WYG1454-072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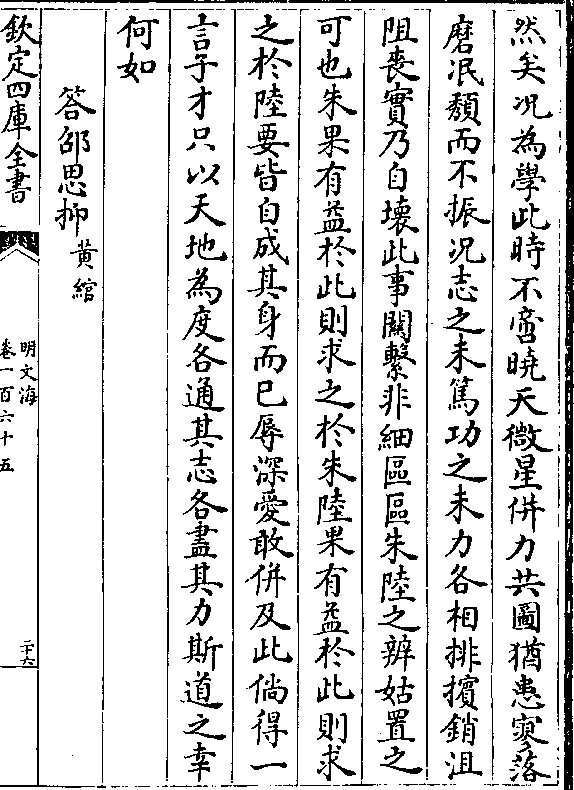 然矣况为学此时不啻晓天微星并力共图犹患寥落
然矣况为学此时不啻晓天微星并力共图犹患寥落磨泯颓而不振况志之未笃功之未力各相排摈销沮
阻丧实乃自坏此事关系非细区区朱陆之辨姑置之
可也朱果有益于此则求之于朱陆果有益于此则求
之于陆要皆自成其身而已辱深爱敢并及此倘得一
言子才只以天地为度各通其志各尽其力斯道之幸
何如
答邵思抑(黄绾/)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6b 页 WYG1454-072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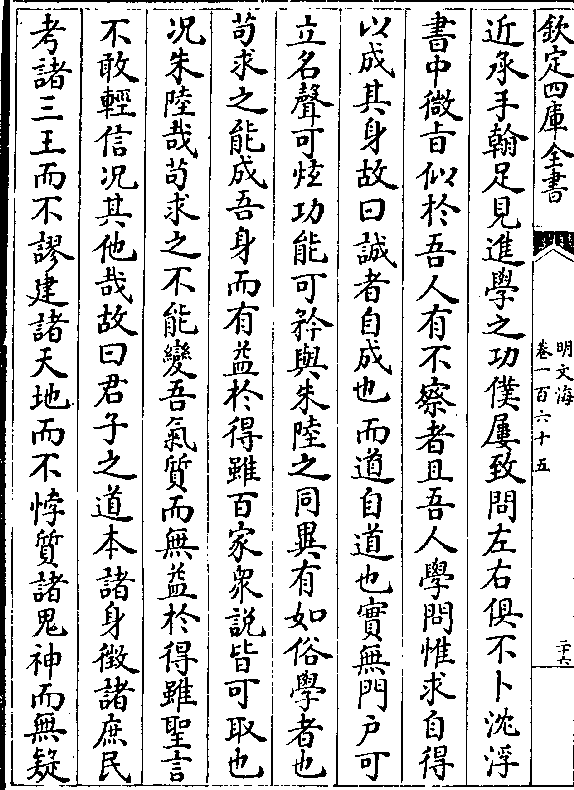 近承手翰足见进学之功仆屡致问左右俱不卜沈浮
近承手翰足见进学之功仆屡致问左右俱不卜沈浮书中微旨似于吾人有不察者且吾人学问惟求自得
以成其身故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实无门户可
立名声可炫功能可矜与朱陆之同异有如俗学者也
苟求之能成吾身而有益于得虽百家众说皆可取也
况朱陆哉苟求之不能变吾气质而无益于得虽圣言
不敢轻信况其他哉故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
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7a 页 WYG1454-072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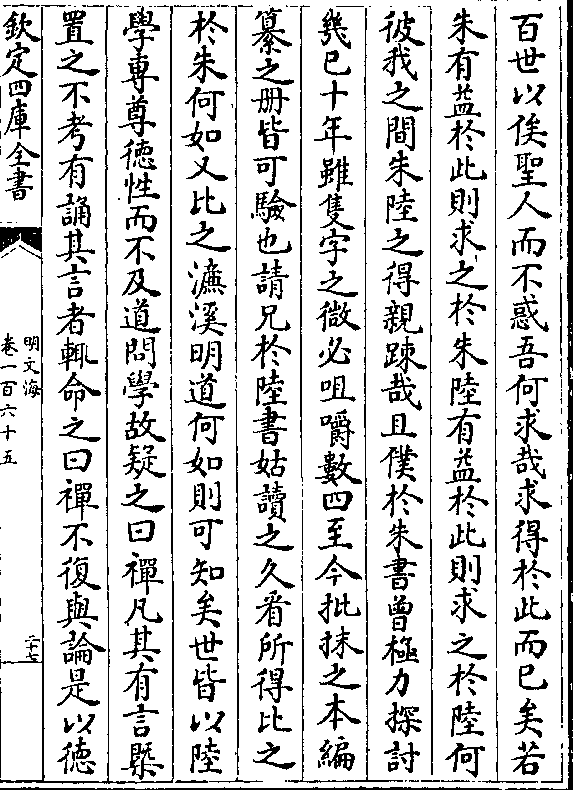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何求哉求得于此而已矣若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何求哉求得于此而已矣若朱有益于此则求之于朱陆有益于此则求之于陆何
彼我之间朱陆之得亲疏哉且仆于朱书曾极力探讨
几已十年虽只字之微必咀嚼数四至今批抹之本编
纂之册皆可验也请兄于陆书姑读之久看所得比之
于朱何如乂比之濂溪明道何如则可知矣世皆以陆
学专尊德性而不及道问学故疑之曰禅凡其有言槩
置之不考有诵其言者辄命之曰禅不复与论是以德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7b 页 WYG1454-072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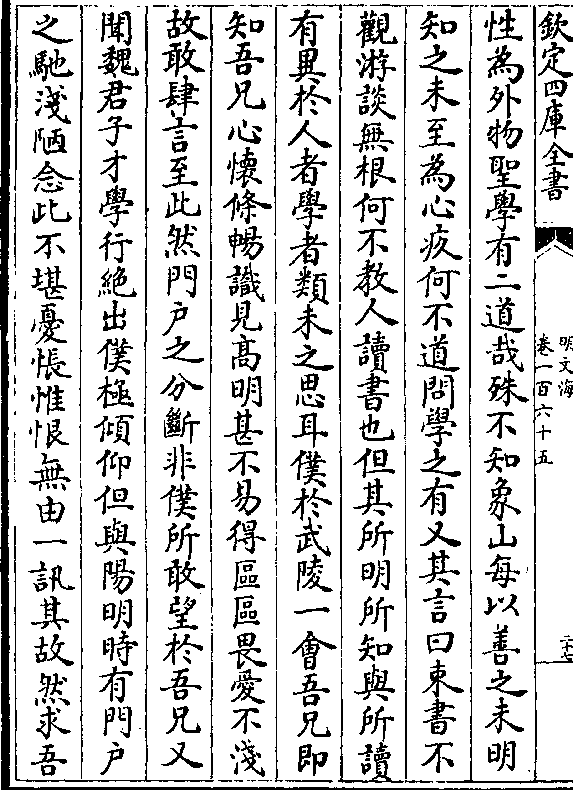 性为外物圣学有二道哉殊不知象山每以善之未明
性为外物圣学有二道哉殊不知象山每以善之未明知之未至为心疚何不道问学之有又其言曰束书不
观游谈无根何不教人读书也但其所明所知与所读
有异于人者学者类未之思耳仆于武陵一会吾兄即
知吾兄心怀条畅识见高明甚不易得区区畏爱不浅
故敢肆言至此然门户之分断非仆所敢望于吾兄又
闻魏君子才学行绝出仆极倾仰但与阳明时有门户
之驰浅陋念此不堪忧怅惟恨无由一讯其故然求吾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8a 页 WYG1454-072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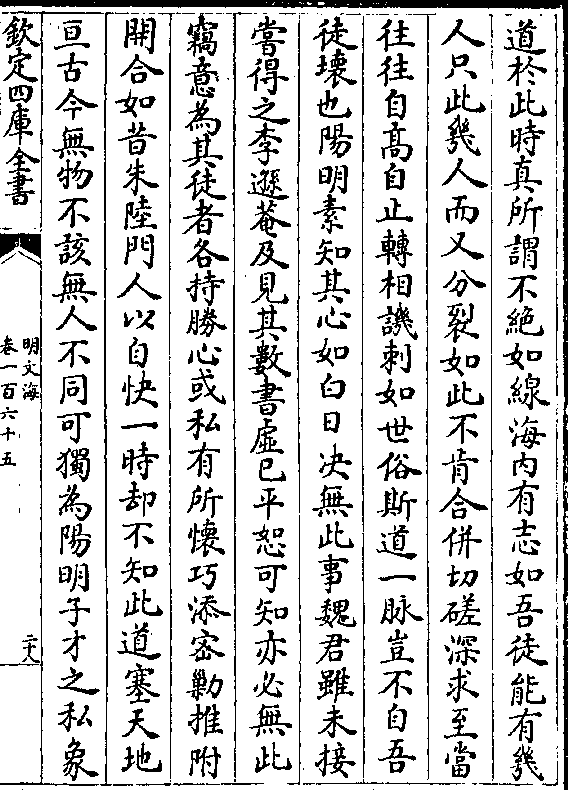 道于此时真所谓不绝如线海内有志如吾徒能有几
道于此时真所谓不绝如线海内有志如吾徒能有几人只此几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并切磋深求至当
往往自高自止转相讥刺如世俗斯道一脉岂不自吾
徒坏也阳明素知其心如白日决无此事魏君虽未接
尝得之李逊庵及见其数书虚已平恕可知亦必无此
窃意为其徒者各持胜心或私有所怀巧添密剿推附
开合如昔朱陆门人以自快一时却不知此道塞天地
亘古今无物不该无人不同可独为阳明子才之私象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8b 页 WYG1454-072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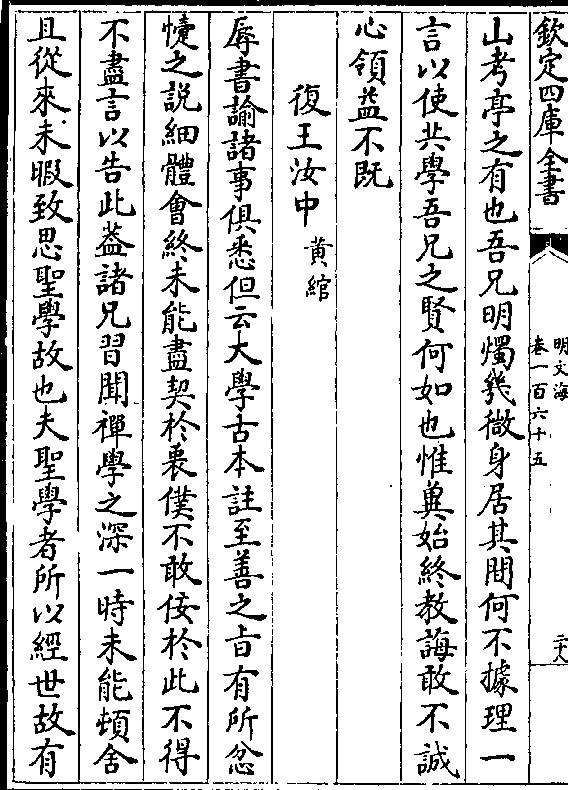 山考亭之有也吾兄明烛几微身居其间何不据理一
山考亭之有也吾兄明烛几微身居其间何不据理一言以使共学吾兄之贤何如也惟冀始终教诲敢不诚
心领益不既
复王汝中(黄绾/)
辱书谕诸事俱悉但云大学古本注至善之旨有所忿
懥之说细体会终未能尽契于衷仆不敢佞于此不得
不尽言以告此盖诸兄习闻禅学之深一时未能顿舍
且从来未暇致思圣学故也夫圣学者所以经世故有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9a 页 WYG1454-0722a.png
 体则必有用有工夫则必有功效此所以齐家而治国
体则必有用有工夫则必有功效此所以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也禅学者所以出世故有体而无用有工夫而
无功效此所以虚寂无所住着而涅槃也故为禅学者
略涉作用稍论功效则为作念而四果皆非谓之有漏
其道不可成矣圣学工夫则在体上做事业则在用与
功效上见故大学首章言大人为学之道提出三在字
以见道之所在在于尽性在于尽伦在止于至善尽性
尽伦必止于至善故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盖尽伦
卷一百六十五 第 29b 页 WYG1454-072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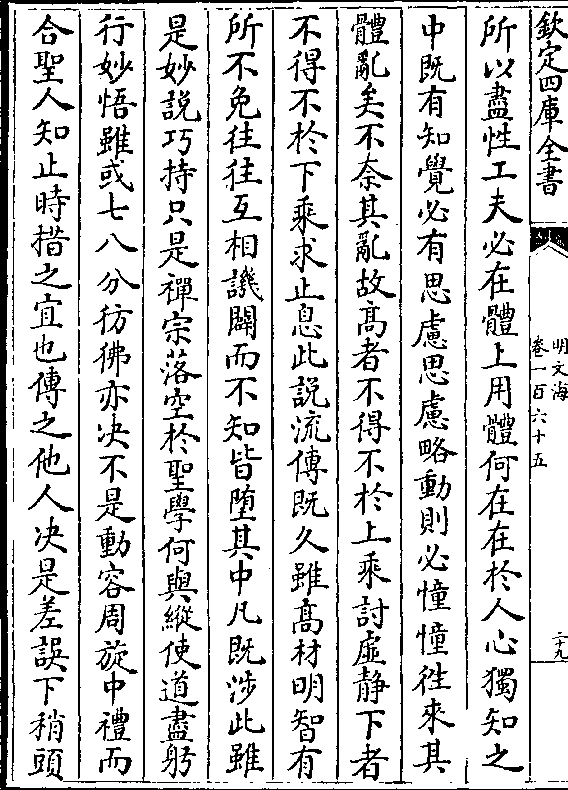 所以尽性工夫必在体上用体何在在于人心独知之
所以尽性工夫必在体上用体何在在于人心独知之中既有知觉必有思虑思虑略动则必憧憧往来其
体乱矣不奈其乱故高者不得不于上乘讨虚静下者
不得不于下乘求止息此说流传既久虽高材明智有
所不免往往互相讥辟而不知皆堕其中凡既涉此虽
是妙说巧持只是禅宗落空于圣学何与纵使道尽躬
行妙悟虽或七八分彷佛亦决不是动容周旋中礼而
合圣人知止时措之宜也传之他人决是差误下稍头
卷一百六十五 第 30a 页 WYG1454-072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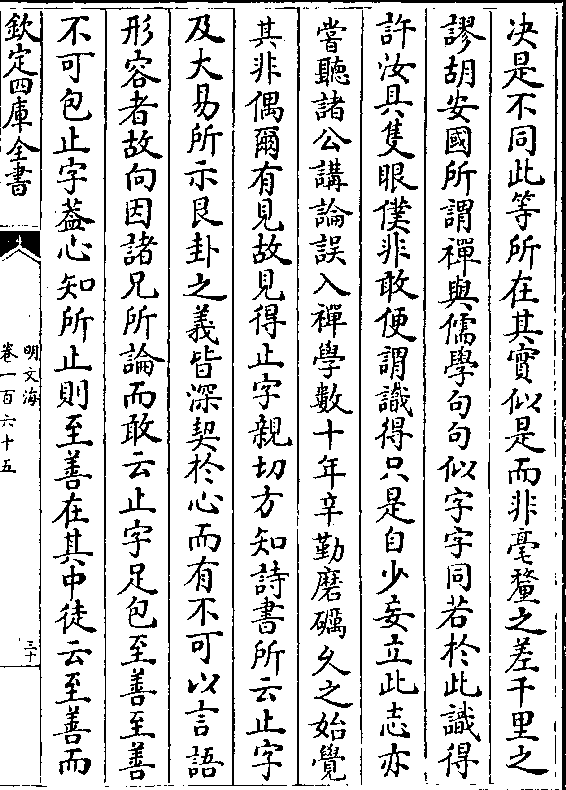 决是不同此等所在其实似是而非毫釐之差千里之
决是不同此等所在其实似是而非毫釐之差千里之谬胡安国所谓禅与儒学句句似字字同若于此识得
许汝具只眼仆非敢便谓识得只是自少妄立此志亦
尝听诸公讲论误入禅学数十年辛勤磨砺久之始觉
其非偶尔有见故见得止字亲切方知诗书所云止字
及大易所示艮卦之义皆深契于心而有不可以言语
形容者故向因诸兄所论而敢云止字足包至善至善
不可包止字盖心知所止则至善在其中徒云至善而
卷一百六十五 第 30b 页 WYG1454-0722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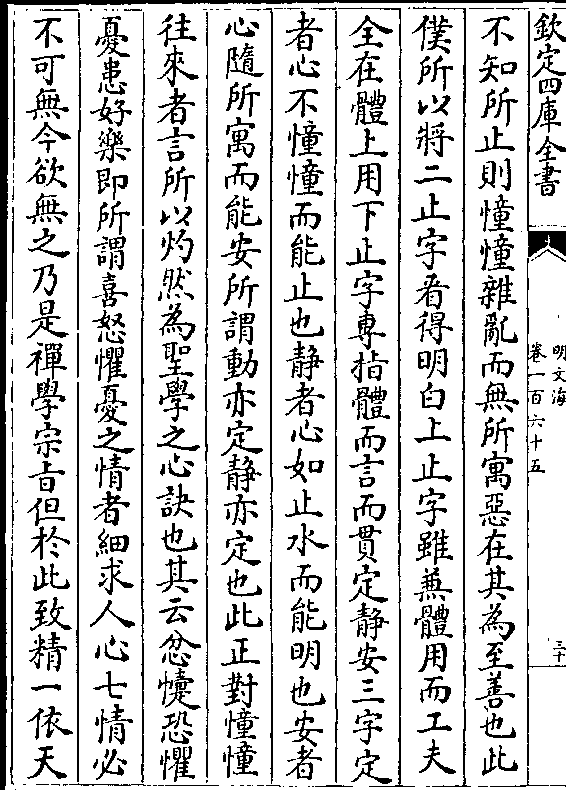 不知所止则憧憧杂乱而无所寓恶在其为至善也此
不知所止则憧憧杂乱而无所寓恶在其为至善也此仆所以将二止字看得明白上止字虽兼体用而工夫
全在体上用下止字专指体而言而贯定静安三字定
者心不憧憧而能止也静者心如止水而能明也安者
心随所寓而能安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也此正对憧憧
往来者言所以灼然为圣学之心诀也其云忿懥恐惧
忧患好乐即所谓喜怒惧忧之情者细求人心七情必
不可无今欲无之乃是禅学宗旨但于此致精一依天
卷一百六十五 第 31a 页 WYG1454-072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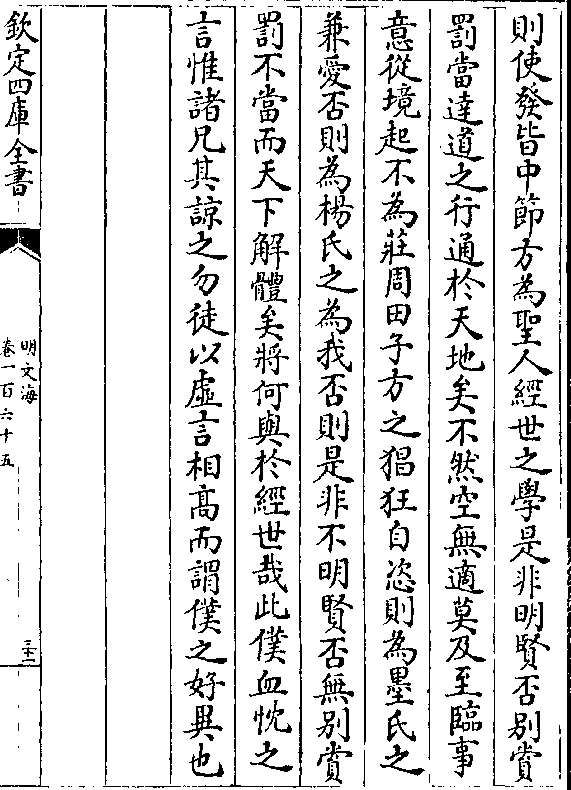 则使发皆中节方为圣人经世之学是非明贤否别赏
则使发皆中节方为圣人经世之学是非明贤否别赏罚当达道之行通于天地矣不然空无适莫及至临事
意从境起不为庄周田子方之猖狂自恣则为墨氏之
兼爱否则为杨氏之为我否则是非不明贤否无别赏
罚不当而天下解体矣将何与于经世哉此仆血忱之
言惟诸兄其谅之勿徒以虚言相高而谓仆之好异也
卷一百六十五 第 31b 页 WYG1454-072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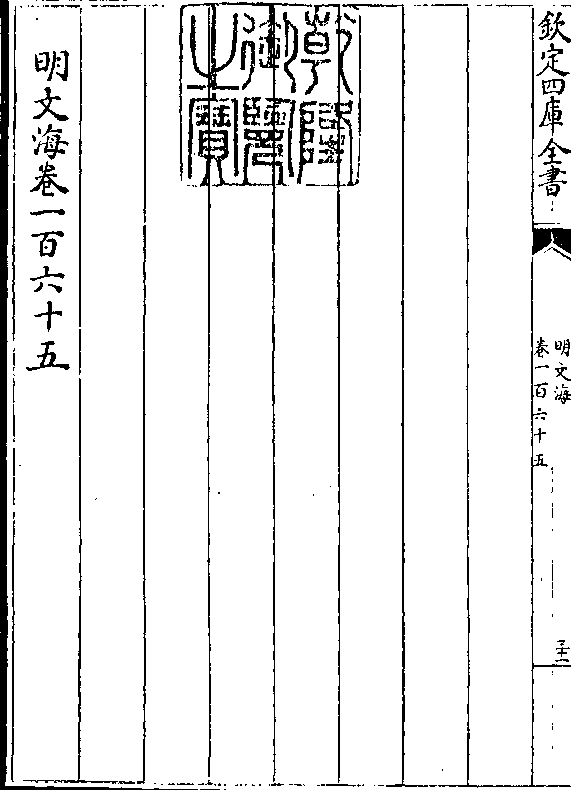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