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石菱集卷五 第 x 页
石菱集卷五
会欣颖[上篇]
会欣颖[上篇]
石菱集卷五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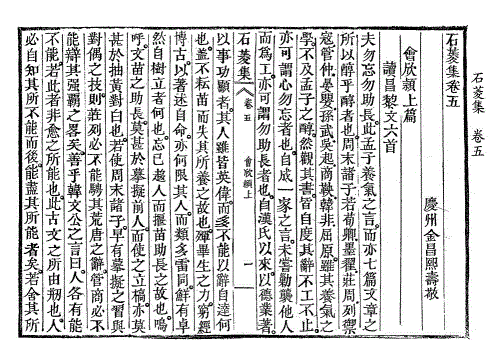 读昌黎文(六首)[其一]
读昌黎文(六首)[其一]夫勿忘勿助长。此孟子养气之言。而亦七篇文章之所以醇乎醇者也。周末诸子若荀卿,墨翟,庄周,列御寇,管仲,晏婴,孙武,吴起,商鞅,韩非,屈原。虽其养气之学。不及孟子之醇。然观其书。皆自度其辞不工不止。亦可谓心勿忘者也。自成一家之言。未尝剿袭他人而为工。亦可谓勿助长者也。自汉氏以来。以德业著。以事功显者。其人虽皆英伟。而多不能以辞自达何也。盖不耘苗而失其所养之故也。殚毕生之力。穷经博古。以著述自命。亦何限其人。而类多雷同。鲜有卓然自树立者何也。忘己趍人而揠苗助长之故也。呜呼。文苗之助长。莫甚于摹拟前人。而使之立槁。亦莫甚于抽黄对白也。若使周末诸子。早有摹拟之习与对偶之技。则庄列必不能骋其荒唐之辞。管商必不能辩其强霸之略矣。善乎韩文公之言曰。人各有能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此古文之所由刱也。人必自知其所不能而后。能尽其所能者矣。若舍其所
石菱集卷五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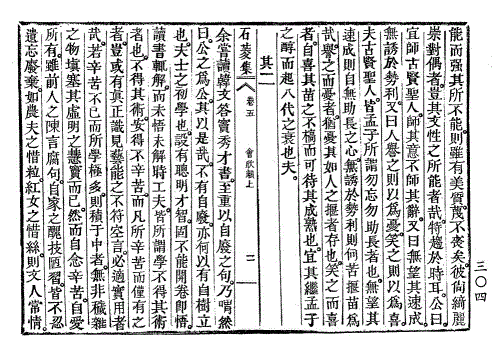 能而强其所不能。则虽有美质。蔑不丧矣。彼尚绮丽崇对偶者。岂其文性之所能者哉。特趋于时耳。公曰。宜师古贤圣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又曰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又曰人誉之则以为忧。笑之则以为喜。夫古贤圣人。皆孟子所谓勿忘勿助长者也。无望其速成则自无助长之心。无诱于势利则何苦揠苗为哉。誉之而忧者。犹忧其如人之揠者存也。笑之而喜者。自喜其苗之不槁而可待其成熟也。宜其继孟子之醇而起八代之衰也夫。
能而强其所不能。则虽有美质。蔑不丧矣。彼尚绮丽崇对偶者。岂其文性之所能者哉。特趋于时耳。公曰。宜师古贤圣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又曰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又曰人誉之则以为忧。笑之则以为喜。夫古贤圣人。皆孟子所谓勿忘勿助长者也。无望其速成则自无助长之心。无诱于势利则何苦揠苗为哉。誉之而忧者。犹忧其如人之揠者存也。笑之而喜者。自喜其苗之不槁而可待其成熟也。宜其继孟子之醇而起八代之衰也夫。读昌黎文[其二]
余尝读韩文答窦秀才书。至重以自废之句。乃喟然曰。公之为公。其以是哉。不有自废。亦何以有自树立也。夫士之初学也。设有聪明才智。固不能开卷即悟。读书辄解。而未悟未解时工夫。皆所谓学不得其术者也。不得其术。安得不辛苦。而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岂或有真正识见艺能之不符空言。必适实用者哉。若辛苦不已而所学极多。则积于中者。无非秽杂之物填塞其虚明之慧窦而已。然而自念辛苦。自爱所有。虽前人之陈言腐句。自家之丑技陋习。皆不忍遗忘废弃。如农夫之惜粒。红女之惜丝。则文人常情。
石菱集卷五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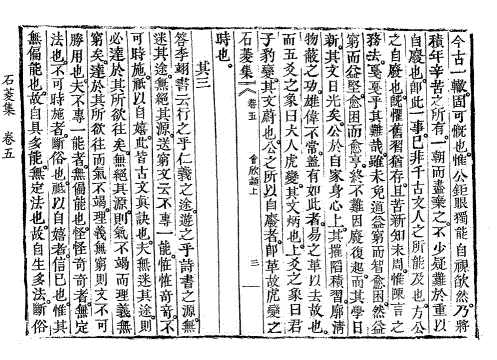 今古一辙。固可慨也。惟公钜眼独能自视欿然。乃将积年辛苦之所有。一朝而尽弃之。不少疑难于重以自废也。即此一事。已非千古文人之所能及也。方公之自废也。既惧旧习犹存。且苦新知未周。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虽未免道益穷而智愈困。然益穷而益坚。愈困而愈亨。终不难因废复起。而其学日新。其文日光矣。公于自家身心上。其摧陷积习。廓清物蔽之功。雄伟不常。盖有如此者。易之革以去故也。而五爻之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爻之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公之所以自废者。即革故虎变之时也。
今古一辙。固可慨也。惟公钜眼独能自视欿然。乃将积年辛苦之所有。一朝而尽弃之。不少疑难于重以自废也。即此一事。已非千古文人之所能及也。方公之自废也。既惧旧习犹存。且苦新知未周。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虽未免道益穷而智愈困。然益穷而益坚。愈困而愈亨。终不难因废复起。而其学日新。其文日光矣。公于自家身心上。其摧陷积习。廓清物蔽之功。雄伟不常。盖有如此者。易之革以去故也。而五爻之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爻之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公之所以自废者。即革故虎变之时也。读昌黎文[其三]
答李翊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送穷文云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此皆古文真诀也。夫无迷其途。则必达于其所欲往矣。无绝其源。则气不竭而理义无穷矣。达于其所欲往而气不竭。理义无穷则文不可胜用也。夫不专一能者。无偏能也。怪怪奇奇者。无定法也。不可时施者。断俗也。祗以自嬉者。信己也。惟其无偏能也。故自具多能。无定法也。故自生多法。断俗
石菱集卷五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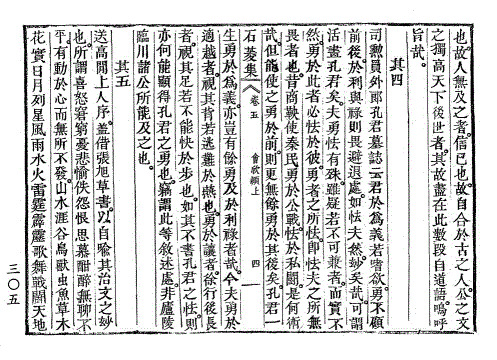 也。故人无及之者。信己也。故自合于古之人。公之文之独高天下后世者。其故尽在此数段自道语。呜呼旨哉。
也。故人无及之者。信己也。故自合于古之人。公之文之独高天下后世者。其故尽在此数段自道语。呜呼旨哉。读昌黎文[其四]
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云君于为义若嗜欲。勇不顾前后。于利与禄则畏避退处。如怯夫然。妙矣哉。可谓活画孔君矣。夫勇怯有殊。虽疑若不可兼者。而实不然。勇于此者必怯于彼。勇者之所怯。即怯夫之所无畏者也。昔商鞅使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是何术哉。但能使之勇于前。则更无馀勇于其后矣。孔君一生勇于为义。亦岂有馀勇及于利禄者哉。今夫勇于适越者。视其背若逃难于燕也。勇于让者。徐行后长者。视其足若不能快于步也。如其不书孔君之怯。则亦何能显得孔君之勇也。窃谓此等叙述处。非庐陵临川诸公所能及之也。
读昌黎文[其五]
送高閒上人序。盖借张旭草书。以自喻其治文之妙也。所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而无所不发。山水涯谷鸟兽虫鱼草木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
石菱集卷五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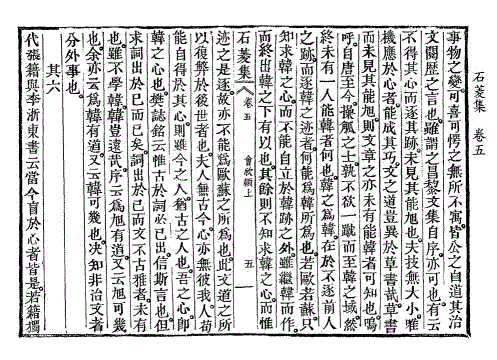 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之无所不寓。皆公之自道其治文阅历之言也。虽谓之昌黎文集自序。亦可也。有云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夫技无大小。唯机应于心者。能成其巧。文之道岂异于草书哉。草书而未见其能旭。则文章之亦未有能韩者可知也。呜呼。自唐至今。操觚之士。孰不欲一蹴而至韩之域。然终未有一人能韩者何也。韩之为韩。在于不逐前人之迹。而逐韩之迹者。何能为韩所为也。若欧若苏。只知求韩之心。而不能自立于韩迹之外。虽继韩而作。而终出韩之下有以也。其馀则不知求韩之心。而惟迹之是逐。故亦不能为欧苏之所为也。此文道之所以复弊于后世者也。夫人无古今。心亦无彼我。人苟能自得于其心。则虽今之人。犹古之人也。吾之心。即韩之心也。樊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信斯言也。但求词出于己而已矣。词出于己而文不古雅者。未有也。虽不学韩。韩岂远哉。序云为旭有道。又云旭可几也。余亦云为韩有道。又云韩可几也。决知非治文者分外事也。
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之无所不寓。皆公之自道其治文阅历之言也。虽谓之昌黎文集自序。亦可也。有云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夫技无大小。唯机应于心者。能成其巧。文之道岂异于草书哉。草书而未见其能旭。则文章之亦未有能韩者可知也。呜呼。自唐至今。操觚之士。孰不欲一蹴而至韩之域。然终未有一人能韩者何也。韩之为韩。在于不逐前人之迹。而逐韩之迹者。何能为韩所为也。若欧若苏。只知求韩之心。而不能自立于韩迹之外。虽继韩而作。而终出韩之下有以也。其馀则不知求韩之心。而惟迹之是逐。故亦不能为欧苏之所为也。此文道之所以复弊于后世者也。夫人无古今。心亦无彼我。人苟能自得于其心。则虽今之人。犹古之人也。吾之心。即韩之心也。樊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信斯言也。但求词出于己而已矣。词出于己而文不古雅者。未有也。虽不学韩。韩岂远哉。序云为旭有道。又云旭可几也。余亦云为韩有道。又云韩可几也。决知非治文者分外事也。读昌黎文[其六]
代张籍与李浙东书云当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独
石菱集卷五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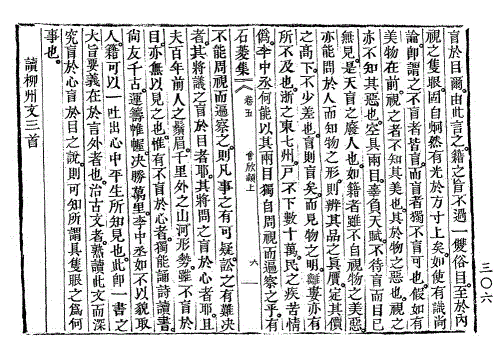 盲于目尔。由此言之。籍之盲不过一双俗目。至于内视之只眼。固自炯然有光于方寸上矣。如使有识尚论。即谓之不盲者皆盲。而盲者独不盲可也。假如有美物在前。视之者不知其美也。其于物之恶也。视之亦不知其恶也。空具两目。辜负天赋。不待盲而目已无见。是天盲之废人也。如籍者虽不自视物之美恶。亦能问于人而知物之形。则辨其品之真赝。定其价之高下。不少差也。盲则盲矣。而见物之明。离娄亦有所不及也。浙之东七州。户不下数十万。民之疾苦情伪。李中丞何能以其两目独自周视而遍察之乎。有不能周视而遍察之。则凡事之有可疑。讼之有难决者。其将议之盲于目者耶。其将问之盲于心者耶。且夫百年前人之须眉。千里外之山河形势。虽不盲于目。亦无以见之也。惟有不盲于心者。独能诵诗读书。尚友千古。运筹帷幄。决胜万里。李中丞如不以貌取人。籍可以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见也。此即一书之大旨要义在于言外者也。治古文者。熟读此文而深究盲于心盲于目之说。则可知所谓具只眼之为何事也。
盲于目尔。由此言之。籍之盲不过一双俗目。至于内视之只眼。固自炯然有光于方寸上矣。如使有识尚论。即谓之不盲者皆盲。而盲者独不盲可也。假如有美物在前。视之者不知其美也。其于物之恶也。视之亦不知其恶也。空具两目。辜负天赋。不待盲而目已无见。是天盲之废人也。如籍者虽不自视物之美恶。亦能问于人而知物之形。则辨其品之真赝。定其价之高下。不少差也。盲则盲矣。而见物之明。离娄亦有所不及也。浙之东七州。户不下数十万。民之疾苦情伪。李中丞何能以其两目独自周视而遍察之乎。有不能周视而遍察之。则凡事之有可疑。讼之有难决者。其将议之盲于目者耶。其将问之盲于心者耶。且夫百年前人之须眉。千里外之山河形势。虽不盲于目。亦无以见之也。惟有不盲于心者。独能诵诗读书。尚友千古。运筹帷幄。决胜万里。李中丞如不以貌取人。籍可以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见也。此即一书之大旨要义在于言外者也。治古文者。熟读此文而深究盲于心盲于目之说。则可知所谓具只眼之为何事也。读柳州文(三首)[其一]
石菱集卷五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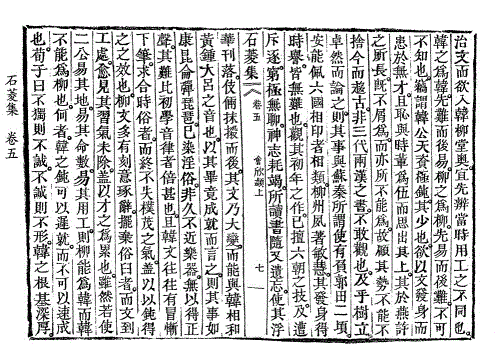 治文而欲入韩柳堂奥。宜先辨当时用工之不同也。韩之为韩。先难而后易。柳之为柳。先易而后难。不可不知也。窃谓韩公天资极钝。其少也。欲以文发身而患于无才。且耻与时辈为伍而思出其上。其于燕许之所长。既不屑为。而亦所不能为。故顾其势不能不舍今而趍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也。及乎树立卓然而论之。则其事与苏秦所谓使有负郭田二顷。安能佩六国相印者相类。柳州夙著敏慧。其发身得时誉。皆无难也。观其初年之作。已擅六朝之技。及遭斥逐。穷极无聊。神志耗竭。所读书随又遗忘。使其浮华刊落。伎俩抹摋而后。其文乃大变。而能与韩相和黄钟大吕之音也。以其毕竟成就而言之。则其事如康昆仑弹琵琶。已染淫俗。非久不近乐器。无以得正声。其难比初学音律者倍甚也。且韩文往往有冒惭下笔。求合时俗者。而终不失朴茂之气。善以以钝得之之效也。柳文多有刻意琢辞。摆弃俗臼者。而文到工处。愈见其习气未除。盖以才之为累也。虽然若使二公易其地。易其命数。易其用工。则柳能为韩而韩不能为柳也。何者。韩之钝可以迟就。而不可以速成也。荀子曰不独则不诚。不诚则不形。韩之根基深厚。
治文而欲入韩柳堂奥。宜先辨当时用工之不同也。韩之为韩。先难而后易。柳之为柳。先易而后难。不可不知也。窃谓韩公天资极钝。其少也。欲以文发身而患于无才。且耻与时辈为伍而思出其上。其于燕许之所长。既不屑为。而亦所不能为。故顾其势不能不舍今而趍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也。及乎树立卓然而论之。则其事与苏秦所谓使有负郭田二顷。安能佩六国相印者相类。柳州夙著敏慧。其发身得时誉。皆无难也。观其初年之作。已擅六朝之技。及遭斥逐。穷极无聊。神志耗竭。所读书随又遗忘。使其浮华刊落。伎俩抹摋而后。其文乃大变。而能与韩相和黄钟大吕之音也。以其毕竟成就而言之。则其事如康昆仑弹琵琶。已染淫俗。非久不近乐器。无以得正声。其难比初学音律者倍甚也。且韩文往往有冒惭下笔。求合时俗者。而终不失朴茂之气。善以以钝得之之效也。柳文多有刻意琢辞。摆弃俗臼者。而文到工处。愈见其习气未除。盖以才之为累也。虽然若使二公易其地。易其命数。易其用工。则柳能为韩而韩不能为柳也。何者。韩之钝可以迟就。而不可以速成也。荀子曰不独则不诚。不诚则不形。韩之根基深厚。石菱集卷五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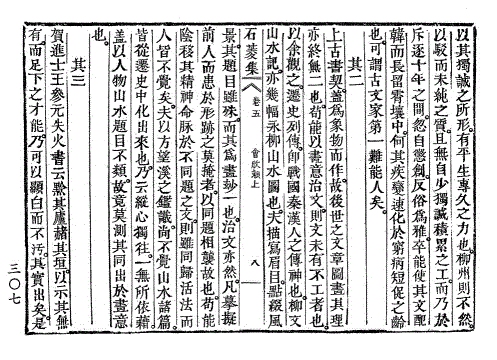 以其独诚之所形。有平生专久之力也。柳州则不然。以驳而未纯之质。且无自少独诚积累之工。而乃于斥逐十年之间。忽自惩创。反俗为雅。卒能使其文配韩而长留霄壤中。何其疾变速化于穷病短促之龄也。可谓古文家第一难能人矣。
以其独诚之所形。有平生专久之力也。柳州则不然。以驳而未纯之质。且无自少独诚积累之工。而乃于斥逐十年之间。忽自惩创。反俗为雅。卒能使其文配韩而长留霄壤中。何其疾变速化于穷病短促之龄也。可谓古文家第一难能人矣。读柳州文[其二]
上古书契。盖为象物而作。故后世之文章图画其理亦终无二也。苟能以画意治文。则文未有不工者也。以余观之。迁史列传。即战国秦汉人之传神也。柳文山水记。亦几幅永柳山水图也。夫描写眉目。点缀风景。其题目虽殊。而其为画妙一也。治文亦然。凡摹拟前人而患于形迹之莫掩者。以同题相袭故也。苟能阴移其精神命脉于不同题之文。则虽同归活法而人皆不觉矣。夫以方望溪之鉴识。尚不觉山水诸篇。皆从迁史中化出来也。乃云纵心独往。一无所依藉。盖以人物山水题目不类。故竟莫测其同出于画意也。
读柳州文[其三]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云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
石菱集卷五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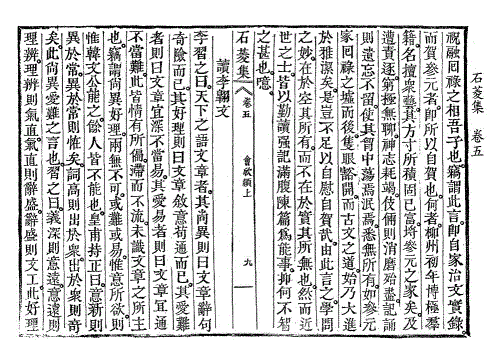 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窃谓此言。即自家治文实录。而贺参元者。即所以自贺也。何者。柳州初年博极群籍。名擅众艺。其方寸所积固已富。埒参元之家矣。及遭责逐。穷极无聊。神志耗竭。伎俩则消磨殆尽。记诵则遗忘不留。使其胸中荡焉泯焉。悉无所有。如参元家回禄之墟而后。只眼豁开。而古文之道。始乃大进于雅洁矣。是岂不足以自慰自贺哉。由此言之。学问之妙。在于空其所有。而不在于实其所无也。然而近世之士。皆以勤读强记满腹陈篇为能事。抑何不智之甚也。噫。
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窃谓此言。即自家治文实录。而贺参元者。即所以自贺也。何者。柳州初年博极群籍。名擅众艺。其方寸所积固已富。埒参元之家矣。及遭责逐。穷极无聊。神志耗竭。伎俩则消磨殆尽。记诵则遗忘不留。使其胸中荡焉泯焉。悉无所有。如参元家回禄之墟而后。只眼豁开。而古文之道。始乃大进于雅洁矣。是岂不足以自慰自贺哉。由此言之。学问之妙。在于空其所有。而不在于实其所无也。然而近世之士。皆以勤读强记满腹陈篇为能事。抑何不智之甚也。噫。读李翱文
李习之曰。天下之语文章者。其尚异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窃谓尚异好理。两无不可。或难或易。惟意所欲。则惟韩文公能之。馀人皆不能也。皇甫持正曰。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此尚异爱难之言也。习之曰。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此好理
石菱集卷五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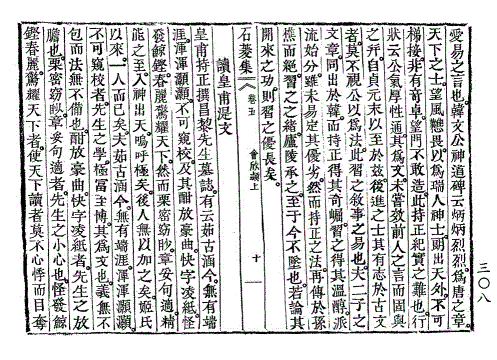 爱易之言也。韩文公神道碑云炳炳烈烈。为唐之章。天下之士。望风戁畏。以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门不敢造。此持正纪实之难也。行状云公气厚性通。其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自贞元末以至于玆。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此习之叙事之易也。夫二子之文章。同出于韩。而持正得其奇崛。习之得其温醇。派流始分。虽未易定其优劣。然而持正之法。再传于孙樵而绝。习之之绪。庐陵承之。至于今不坠也。若论其开来之功。则习之优长矣。
爱易之言也。韩文公神道碑云炳炳烈烈。为唐之章。天下之士。望风戁畏。以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望门不敢造。此持正纪实之难也。行状云公气厚性通。其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自贞元末以至于玆。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此习之叙事之易也。夫二子之文章。同出于韩。而持正得其奇崛。习之得其温醇。派流始分。虽未易定其优劣。然而持正之法。再传于孙樵而绝。习之之绪。庐陵承之。至于今不坠也。若论其开来之功。则习之优长矣。读皇甫湜文
皇甫持正撰昌黎先生墓志。有云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夫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者。先生之学。极富至博。其为文也。义无不包而法无不备也。酣放豪曲。快字凌纸者。先生之放胆也。栗密窈眇。章妥句适者。先生之小心也。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者。使天下读者莫不心悸而目夺
石菱集卷五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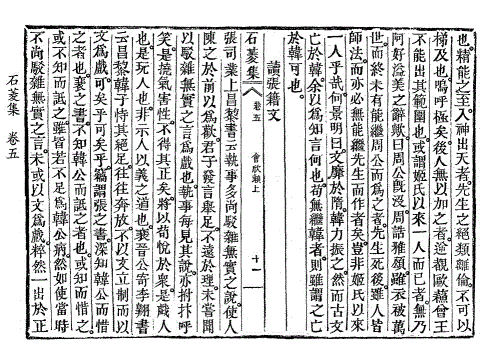 也。精能之至。入神出天者。先生之绝类离伦。不可以梯及也。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者。逆睹欧苏曾王不能出其范围也。或谓姬氏以来一人而已者。无乃阿好溢美之辞欤。曰周公既没。周诰雅颂。虽衣被万世。而终未有能继周公而为之者。先生死后。虽人皆师法。而亦必无能继先生而作者矣。岂非姬氏以来一人乎哉。何景明曰。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而古文亡于韩。余以为知言何也。苟无继韩者。则虽谓之亡于韩可也。
也。精能之至。入神出天者。先生之绝类离伦。不可以梯及也。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者。逆睹欧苏曾王不能出其范围也。或谓姬氏以来一人而已者。无乃阿好溢美之辞欤。曰周公既没。周诰雅颂。虽衣被万世。而终未有能继周公而为之者。先生死后。虽人皆师法。而亦必无能继先生而作者矣。岂非姬氏以来一人乎哉。何景明曰。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而古文亡于韩。余以为知言何也。苟无继韩者。则虽谓之亡于韩可也。读张籍文
张司业上昌黎书云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言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将以苟悦于众。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裴晋公寄李翱书云昌黎韩子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窃谓张之书。深知韩公而惜之者也。裴之书。不知韩公而诋之者也。或知而惜之。或不知而诋之。虽皆若不足为韩公病。然如使当时不尚驳杂无实之言。未或以文为戏。粹然一出于正
石菱集卷五 第 309L 页
 者。必当跨汉越秦。上追雅颂诰誓。奚止为冠于唐宋八家而已哉。尝读毛颖传。信乎其驳杂无实也。送孟东野序。信乎其以文为戏也。梁昭明太子谓陶徵士閒情赋。是白玉微瑕。余于韩集中毛颖传,送孟东野序亦云。
者。必当跨汉越秦。上追雅颂诰誓。奚止为冠于唐宋八家而已哉。尝读毛颖传。信乎其驳杂无实也。送孟东野序。信乎其以文为戏也。梁昭明太子谓陶徵士閒情赋。是白玉微瑕。余于韩集中毛颖传,送孟东野序亦云。读李汉文
李南纪撰昌黎先生文集序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匀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悯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夫诡然而蛟龙翔。先生之蓄于中者不可测也。蔚然而虎凤跃。先生之著于外者异于凡也。锵然而韶匀鸣。先生之声调也。日光玉洁。先生之光辉也。周情孔思。先生之学有所自也。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先生之极博能多而不失其统也。洞视万古。先生之目见也。悯恻当世。先生之心识也。大拯颓风。先生之口辩也。教人自为。先生之手法也。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之出群绝俗也。志益坚。先生之信道笃也。终而翕然随以定。先生之为天下万世所信服也。自唐至今。治古文而窥
石菱集卷五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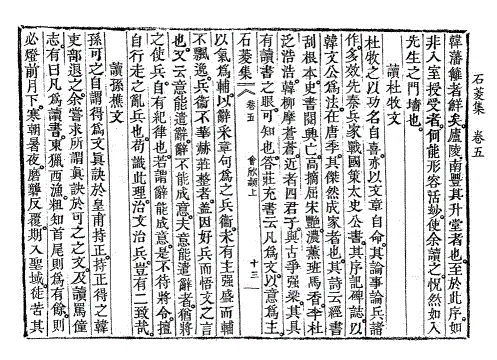 韩藩篱者鲜矣。庐陵,南丰其升堂者也。至于此序。如非入室授受者。何能形容活妙。使余读之。恍然如入先生之门墙也。
韩藩篱者鲜矣。庐陵,南丰其升堂者也。至于此序。如非入室授受者。何能形容活妙。使余读之。恍然如入先生之门墙也。读杜牧文
杜牧之以功名自喜。亦以文章自命。其论事论兵诸作。多效先秦兵家战国策太史公书。其序记碑志。以韩文公为法。在唐季。其杰然成家者也。其诗云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其具有读书之眼。可知也。答庄充书云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兵卫不华赫庄整者。盖因好兵而悟文之言也。又云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夫意能遣辞者。犹将之使兵。自有纪律也。若谓辞能成意。是不待将令。擅自行走之乱兵也。苟识此理。治文治兵。岂有二致哉。
读孙樵文
孙可之自谓得为文真诀于皇甫持正。持正得之韩吏部退之。余尝求所谓真诀于可之之文。及读骂僮志。有曰凡为读书。东猎西渔。粗知首尾则为有馀。则必灯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砻反覆。期入圣域。徒苦其
石菱集卷五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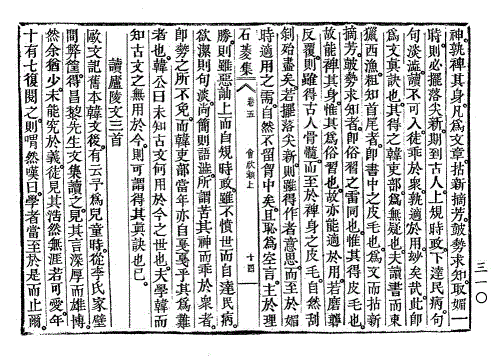 神。孰裨其身。凡为文章。拈新摘芳。鼓势求知。取媚一时。则必摆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规时政。下达民病。句句淡涩。读不可入。徒乖于众。孰适于用。妙矣哉。此即为文真诀也。其得之韩吏部。为无疑也。夫读书而东猎西渔。粗知首尾者。即书中之皮毛也。为文而拈新摘芳。鼓势求知者。即俗习之雷同也。惟其得皮毛也。故能裨其身。惟其为俗习也。故亦能适于用。若磨砻反覆。则虽得古人骨髓。而至于裨身之皮毛。自然刮剥殆尽矣。若摆落尖新。则虽得作者意思。而至于媚时适用之需。自然不留胸中矣。且耻为空言。主于理胜。则虽恶讪上而自规时政。虽不愤世而自达民病。欲洁则句淡。尚简则语涩。所谓苦其神而乖于众者。即势之所不免。而韩吏部当年亦自戛戛乎其为难者也。韩公曰未知古文何用于今之世也。夫学韩而知古文之无用于今。则可谓得其真诀也已。
神。孰裨其身。凡为文章。拈新摘芳。鼓势求知。取媚一时。则必摆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规时政。下达民病。句句淡涩。读不可入。徒乖于众。孰适于用。妙矣哉。此即为文真诀也。其得之韩吏部。为无疑也。夫读书而东猎西渔。粗知首尾者。即书中之皮毛也。为文而拈新摘芳。鼓势求知者。即俗习之雷同也。惟其得皮毛也。故能裨其身。惟其为俗习也。故亦能适于用。若磨砻反覆。则虽得古人骨髓。而至于裨身之皮毛。自然刮剥殆尽矣。若摆落尖新。则虽得作者意思。而至于媚时适用之需。自然不留胸中矣。且耻为空言。主于理胜。则虽恶讪上而自规时政。虽不愤世而自达民病。欲洁则句淡。尚简则语涩。所谓苦其神而乖于众者。即势之所不免。而韩吏部当年亦自戛戛乎其为难者也。韩公曰未知古文何用于今之世也。夫学韩而知古文之无用于今。则可谓得其真诀也已。读庐陵文(三首)[其一]
欧文记旧本韩文后。有云予为儿童时。从李氏家壁间弊筐。得昌黎先生文集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余犹少。未能究于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年十有七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
石菱集卷五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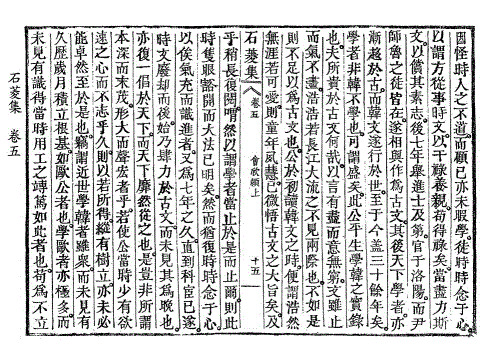 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念于心。以谓方从事时文。以干禄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趍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馀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此公平生学韩之实录也。夫所贵于古文何哉。以言有尽而意无穷。文虽止而气不尽。浩浩若长江大流之不见两际也。不如是则不足以为古文也。公于初读韩文之时。便谓浩然无涯若可爱。则童年夙慧。已微悟古文之大旨矣。及乎稍长复阅。喟然以谓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则此时只眼豁开而大法已明矣。然而犹复时时念于心。以俟气充而识进者。又为七年之久。直到科宦已遂。时文废却而后。始乃肆力于古文。而未见其为晚也。亦复一倡于天下。而天下靡然从之也。是岂非所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者乎。若使公当时少有欲速之心而不志乎久。则以若所得。纵有树立。亦未必能卓然至于是也。窃谓近世学韩者虽众。而未见有久历岁月积立根基。如欧公者也。学欧者亦极多。而未见有识得当时用工之竱笃如此者也。苟为不立
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念于心。以谓方从事时文。以干禄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趍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馀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此公平生学韩之实录也。夫所贵于古文何哉。以言有尽而意无穷。文虽止而气不尽。浩浩若长江大流之不见两际也。不如是则不足以为古文也。公于初读韩文之时。便谓浩然无涯若可爱。则童年夙慧。已微悟古文之大旨矣。及乎稍长复阅。喟然以谓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则此时只眼豁开而大法已明矣。然而犹复时时念于心。以俟气充而识进者。又为七年之久。直到科宦已遂。时文废却而后。始乃肆力于古文。而未见其为晚也。亦复一倡于天下。而天下靡然从之也。是岂非所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者乎。若使公当时少有欲速之心而不志乎久。则以若所得。纵有树立。亦未必能卓然至于是也。窃谓近世学韩者虽众。而未见有久历岁月积立根基。如欧公者也。学欧者亦极多。而未见有识得当时用工之竱笃如此者也。苟为不立石菱集卷五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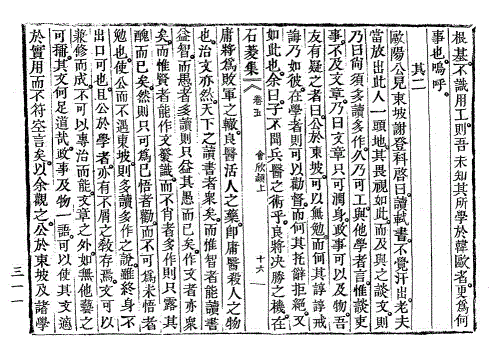 根基。不识用工。则吾未知其所学于韩欧者。更为何事也。呜呼。
根基。不识用工。则吾未知其所学于韩欧者。更为何事也。呜呼。读庐陵文[其二]
欧阳公见东坡谢登科启曰。读轼书。不觉汗出。老夫当放出此人一头地。其畏视如此。而及与之谈文。则乃曰尚须多读多作。久乃可工。与他学者言。惟谈吏事。不及文章。乃曰文章只可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友有疑之者曰。公于东坡。可以无勉。而何其谆谆戒诲乃如彼。在学者则可以劝督。而何其托辞拒绝。又如此也。余曰。子不闻兵医之术乎。良将决胜之机。在庸将为败军之辙。良医活人之药。即庸医杀人之物也。治文亦然。天下之读书者众矣。而惟智者能读书益智。而愚者多读则只益其愚而已矣。作文者亦众矣。而惟贤者能作文发识。而不肖者多作则只露其丑而已矣。然则只可为已悟者劝。而不可为未悟者勉也。使公而不遇东坡。则多读多作之说。虽终身不出口可也。且公于学者。亦有不屑之教存焉。文可以兼修而成。不可以专治而能。文章之外。如无他艺之可称。其文何足道哉。政事及物一语。可以使其文适于实用而不符空言矣。以余观之。公于东坡及诸学
石菱集卷五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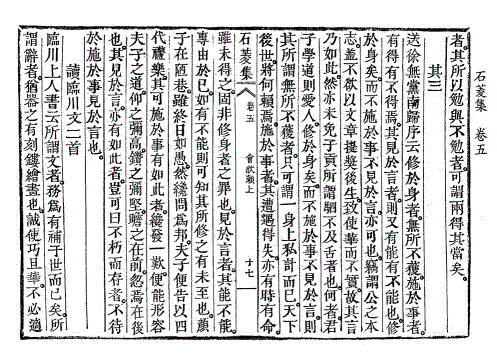 者。其所以勉与不勉者。可谓两得其当矣。
者。其所以勉与不勉者。可谓两得其当矣。读庐陵文[其三]
送徐无党南归序云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窃谓公之本志。盖不欲以文章提奖后生。致使华而不实。故其言乃如此。然亦未免子贡所谓驷不及舌者也。何者。君子学道则爱人。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则其所谓无所不获者。只可谓一身上私计而已。天下后世。将何赖焉。施于事者。其遭遇得失。亦有时有命。虽未得之。固非修身者之罪也。见于言者。其能不能。专由于己。如有不能则可知其所修之有未至也。颜子在陋巷。虽终日如愚。然才问为邦。夫子便告以四代礼乐。其可施于事有如此者。才发一叹。便能形容夫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其见于言。亦有如此者。岂可曰不朽而存者。不待于施于事见于言也。
读临川文(二首)[其一]
临川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
石菱集卷五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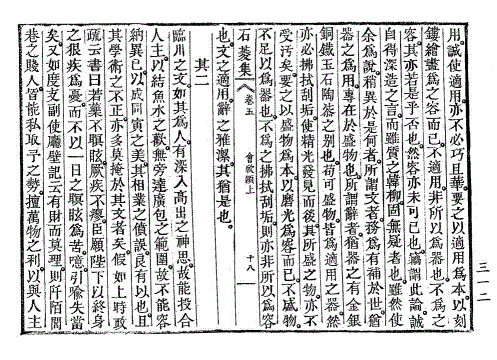 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窃谓此论。诚自得深造之言。而虽质之韩柳。固无疑者也。虽然使余为说。稍异于是何者。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犹器之为用。专在于盛物也。所谓辞者。犹器之有金银铜铁玉石陶漆之别也。苟可盛物。皆为适用之器。然亦必拂拭刮垢。使精光发见而后。其所盛之物。亦不受污矣。要之以盛物为本。以磨光为容而已。不盛物。不足以为器也。不为之拂拭刮垢。则亦非所以为容也。文之适用。辞之雅洁。其犹是也。
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窃谓此论。诚自得深造之言。而虽质之韩柳。固无疑者也。虽然使余为说。稍异于是何者。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犹器之为用。专在于盛物也。所谓辞者。犹器之有金银铜铁玉石陶漆之别也。苟可盛物。皆为适用之器。然亦必拂拭刮垢。使精光发见而后。其所盛之物。亦不受污矣。要之以盛物为本。以磨光为容而已。不盛物。不足以为器也。不为之拂拭刮垢。则亦非所以为容也。文之适用。辞之雅洁。其犹是也。读临川文[其二]
临川之文。如其为人。有深入高出之神思。故能投合人主。以结鱼水之欢。无旁达广包之范围。故不能容纳异己。以成同寅之美。其相业之偾误。良有以也。且其学术之不正。亦多莫掩于其文者矣。假如上时政疏云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狠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噫。引喻失当矣。又如度支副使厅壁记云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
石菱集卷五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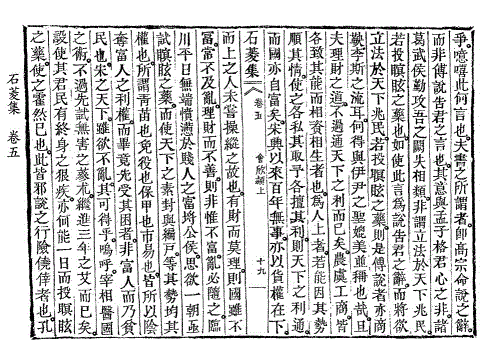 争。噫嘻此何言也。夫书之所谓者。即高宗命说之辞。而非傅说告君之言也。其意与孟子格君心之非。诸葛武侯勤攻吾之阙失相类。非谓立法于天下兆民。若投瞑眩之药也。如使此言为说告君之辞。而将欲立法于天下兆民。若投瞑眩之药。则是傅说者亦商鞅,李斯之流耳。何得与伊尹之圣媲美并称也哉。且夫理财之道。不过通天下之利而已矣。农虞工商。皆各致其能而相资相生者也。为人上者。若能因其势顺其情。使之各私其取予各擅其利。则天下之利通。而国亦自富矣。宋兴以来百年无事。亦以货权在下。而上之人未尝操纵之故也。有财而莫理。则国虽不富。常不及乱。理财而不善。则非惟不富。乱必随之。临川平日无端愤懑于贱人之富埒公侯。思欲一朝亟试瞑眩之药。而使天下之素封与编户。等其势均其权也。所谓青苗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皆所以阴夺富人之利权。而毕竟先受其困者。非富人而乃贫民也。宋之天下。虽欲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宰相医国之术。不过先试无害之蔘朮。继进三年之艾而已矣。设使其君民有终身之狠疾。亦何能一日而投瞑眩之药。使之霍然已也。此皆邪说之行险侥倖者也。孔
争。噫嘻此何言也。夫书之所谓者。即高宗命说之辞。而非傅说告君之言也。其意与孟子格君心之非。诸葛武侯勤攻吾之阙失相类。非谓立法于天下兆民。若投瞑眩之药也。如使此言为说告君之辞。而将欲立法于天下兆民。若投瞑眩之药。则是傅说者亦商鞅,李斯之流耳。何得与伊尹之圣媲美并称也哉。且夫理财之道。不过通天下之利而已矣。农虞工商。皆各致其能而相资相生者也。为人上者。若能因其势顺其情。使之各私其取予各擅其利。则天下之利通。而国亦自富矣。宋兴以来百年无事。亦以货权在下。而上之人未尝操纵之故也。有财而莫理。则国虽不富。常不及乱。理财而不善。则非惟不富。乱必随之。临川平日无端愤懑于贱人之富埒公侯。思欲一朝亟试瞑眩之药。而使天下之素封与编户。等其势均其权也。所谓青苗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皆所以阴夺富人之利权。而毕竟先受其困者。非富人而乃贫民也。宋之天下。虽欲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宰相医国之术。不过先试无害之蔘朮。继进三年之艾而已矣。设使其君民有终身之狠疾。亦何能一日而投瞑眩之药。使之霍然已也。此皆邪说之行险侥倖者也。孔石菱集卷五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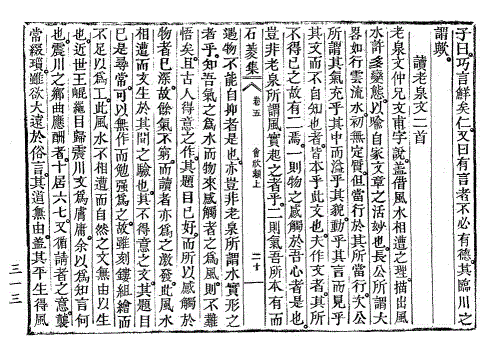 子曰。巧言鲜矣仁。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其临川之谓欤。
子曰。巧言鲜矣仁。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其临川之谓欤。读老泉文(二首)[其一]
老泉文仲兄文甫字说。盖借风水相遭之理。描出风水许多变态。以喻自家文章之活妙也。长公所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其所当行。次公所谓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者。皆本乎此文也。夫作文者。其所不得已之故有二焉。一则物之感触于吾心者是也。岂非老泉所谓风实起之者乎。二则气吾所本有而遇物不能自抑者是也。亦岂非老泉所谓水实形之者乎。知吾气之为水而物来感触者之为风。则不难悟矣。且古人得意之作。其题目已好。而所以感触于物者已深。故馀气不穷。而读者亦为之激发。此风水相遭而文生于其间之验也。其不得意之文。其题目已是寻常。可以无作而勉强为之。故虽刻镂组绘而不足以为工。此风水不相遭而自然之文无由以生也。近世王昆绳目归震川文为肤庸。余以为知言何也。震川之乡曲应酬者。十居六七。又循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盖其平生得风
石菱集卷五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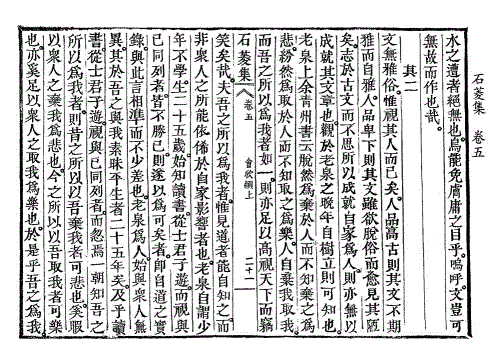 水之遭者绝无也。乌能免肤庸之目乎。呜呼。文岂可无故而作也哉。
水之遭者绝无也。乌能免肤庸之目乎。呜呼。文岂可无故而作也哉。读老泉文[其二]
文无雅俗。惟视其人而已矣。人品高古则其文不期雅而自雅。人品卑下则其文虽欲脱俗而愈见其陋矣。志于古文而不思所以成就自家为人。则亦无以成就其文章也。观于老泉之晚年自树立则可知也。老泉上余青州书云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夫吾之所以为我者。惟见道者能自知之。而非众人之所能依俙于自家影响者也。老泉自谓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者。即自道之实录。与此言相准而不少差也。老泉为人。始与众人无异。其于吾之与我素昧平生者二十五年矣。及乎读书。从士君子游。视与己同列者。而忽焉一朝知吾之所以为我者。则昔之所以以吾弃我者可悲也。奚暇以众人之弃我为悲也。今之所以以吾取我者可乐也。亦奚足以众人之取我为乐也。于是乎吾之为我。
石菱集卷五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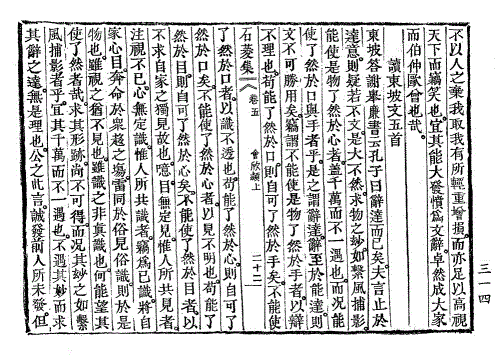 不以人之弃我取我有所轻重增损。而亦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也。宜其能大发愤为文辞。卓然成大家而伯仲欧曾也哉。
不以人之弃我取我有所轻重增损。而亦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也。宜其能大发愤为文辞。卓然成大家而伯仲欧曾也哉。读东坡文(五首)[其一]
东坡答谢举廉书云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窃谓不能使是物了然于手者。以辩不理也。苟能了然于口。则自可了然于手矣。不能使了然于口者。以识不透也。苟能了然于心。则自可了然于口矣。不能使了然于心者。以见不明也。苟能了然于目。则自可了然于心矣。不能使了然于目者。以不求自家之独见故也。噫。目无定见。惟人所共见者。注视不已。心无定识。惟人所共识者。窃为己识。将自家心目。奔命于众趍之场。雷同于俗见俗识。则于是物也。虽视之犹不见也。虽识之非真识也。何能望其使了然者哉。求其形迹。尚不可得。而况其妙之如系风捕影者乎。宜其千万而不一遇也。不遇其妙而求其辞之达。无是理也。公之此言。诚发前人所未发。但
石菱集卷五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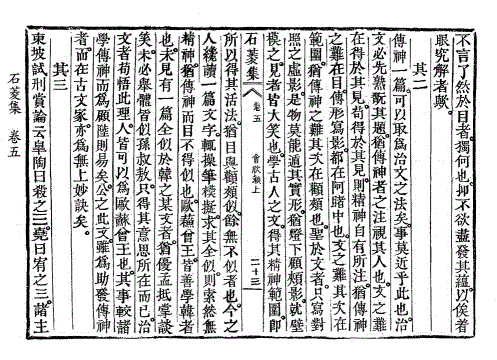 不言了然于目者。独何也。抑不欲尽发其蕴。以俟着眼究解者欤。
不言了然于目者。独何也。抑不欲尽发其蕴。以俟着眼究解者欤。读东坡文[其二]
传神一篇。可以取为治文之法矣。事莫近乎此也。治文必先熟玩其题。犹传神者之注视其人也。文之难在得于其见。苟得于其见。则精神自有所注。犹传神之难在目。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中也。文之难其次在范围。犹传神之难其次在颧颊也。圣于文者。只写对照之虚影。是物莫能遁其实形。犹灯下顾颊影。就壁模之。见者皆大笑也。学古人之文。得其精神范围。即所以得其活法。犹目与颧颊似。馀无不似者也。今之人才读一篇文字。辄操笔模拟。求其全似。则索然无精神。犹传神而目不得似也。欧苏曾王。皆善学韩者也。未见有一篇全似于韩之某文者。犹优孟抵掌谈笑。未必举体皆似孙叔敖。只得其意思所在而已。治文者苟悟此理。人皆可以为欧苏曾王也。其事较诸学传神而为顾陆则易矣。公之此文。虽为助发传神者。而在古文家。亦为无上妙诀矣。
读东坡文[其三]
东坡试刑赏论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
石菱集卷五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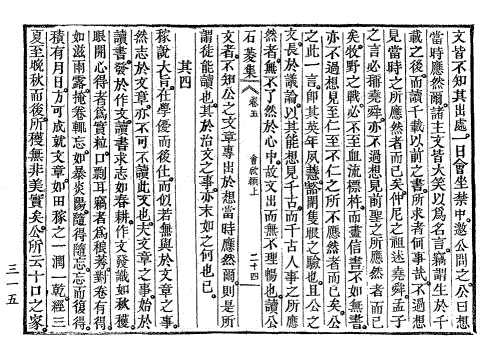 文皆不知其出处。一日会坐禁中。邀公问之。公曰想当时应然尔。诸主文皆大笑以为名言。窃谓生于千载之后。而读千载以前之书。所求者何事哉。不过想见当时之所应然者而已矣。仲尼之祖述尧舜。孟子之言必称尧舜。亦不过想见前圣之所应然者而已矣。牧野之战。必不至血流标杵。而尽信书不如无书。亦不过想见至仁至不仁之所不应然者而已矣。公之此一言。即其英年夙慧。豁开只眼之验也。且公之文。长于议论。以其能想见千古。而千古人事之所应然者。无不了然于心中。故文出而无不理畅也。读公文者。不知公之文章专出于想当时应然尔。则是所谓徒能读也。其于治文之事。亦末如之何也已。
文皆不知其出处。一日会坐禁中。邀公问之。公曰想当时应然尔。诸主文皆大笑以为名言。窃谓生于千载之后。而读千载以前之书。所求者何事哉。不过想见当时之所应然者而已矣。仲尼之祖述尧舜。孟子之言必称尧舜。亦不过想见前圣之所应然者而已矣。牧野之战。必不至血流标杵。而尽信书不如无书。亦不过想见至仁至不仁之所不应然者而已矣。公之此一言。即其英年夙慧。豁开只眼之验也。且公之文。长于议论。以其能想见千古。而千古人事之所应然者。无不了然于心中。故文出而无不理畅也。读公文者。不知公之文章专出于想当时应然尔。则是所谓徒能读也。其于治文之事。亦末如之何也已。读东坡文[其四]
稼说大旨。在学优而后仕。而似若无与于文章之事。然志于文章。亦不可不读此文也。夫文章之事。始于读书。发于作文。读书求志如春耕。作文发识如秋穫。眼开心得者为实粒。口剽耳窃者为稂莠。对卷有得。如滋雨露。掩卷辄忘。如暴炎阳。随得随忘。忘而复得。积有月日。方可成就文章。如田稼之一润一乾。经三夏至晚秋而后。所穫无非美实矣。公所云十口之家。
石菱集卷五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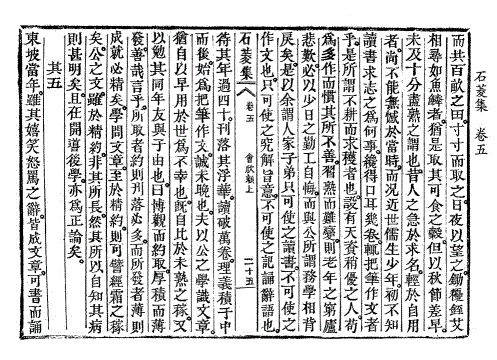 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相寻如鱼鳞者。犹是取其可食之谷。但以秋节差早。未及十分尽熟之谓也。昔人之急于求名。轻于自用者。尚不能无憾于当时。而况近世儒生少年。初不知读书求志之为何事。才得口耳几卷。辄把笔作文者乎。是所谓不耕而求穫者也。设有天资稍优之人。苟为多作而惯其所不善。习熟而难变。则老年之穷庐悲叹。必以少日之勤工自悔。而与公所谓务学相背戾矣。是以余谓人家子弟只可使之读书。不可使之作文也。只可使之究解旨意。不可使之记诵辞语也。待其年过四十。刊落其浮华。读破万卷。理义积于中而后。始为把笔作文。诚未晚也。夫以公之学识文章。犹自以早用于世为不幸也。既自比于未熟之稼。又以勉其同年友与子由也。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善哉言乎。所取者约则刊落必多。而所发者薄则成就必精矣。学问文章。至于精约。则可譬经霜之稼矣。公之文。虽于精约。非其所长。然其所以自知其病则甚明矣。且在开道后学。亦为正论矣。
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相寻如鱼鳞者。犹是取其可食之谷。但以秋节差早。未及十分尽熟之谓也。昔人之急于求名。轻于自用者。尚不能无憾于当时。而况近世儒生少年。初不知读书求志之为何事。才得口耳几卷。辄把笔作文者乎。是所谓不耕而求穫者也。设有天资稍优之人。苟为多作而惯其所不善。习熟而难变。则老年之穷庐悲叹。必以少日之勤工自悔。而与公所谓务学相背戾矣。是以余谓人家子弟只可使之读书。不可使之作文也。只可使之究解旨意。不可使之记诵辞语也。待其年过四十。刊落其浮华。读破万卷。理义积于中而后。始为把笔作文。诚未晚也。夫以公之学识文章。犹自以早用于世为不幸也。既自比于未熟之稼。又以勉其同年友与子由也。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善哉言乎。所取者约则刊落必多。而所发者薄则成就必精矣。学问文章。至于精约。则可譬经霜之稼矣。公之文。虽于精约。非其所长。然其所以自知其病则甚明矣。且在开道后学。亦为正论矣。读东坡文[其五]
东坡当年。虽其嬉笑怒骂之辞。皆成文章。可书而诵
石菱集卷五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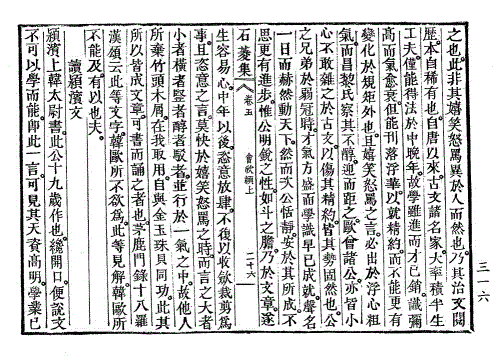 之也。此非其嬉笑怒骂异于人而然也。乃其治文阅历。本自稀有也。自唐以来。古文诸名家。大率积半生工夫。仅能得法于中晚年。故学虽进而才已销。识弥高而气愈衰。但能刊落浮华。以就精约。而不能更有变化于规矩外也。且嬉笑怒骂之言。必出于浮心粗气。而昌黎氏察其不醇。迎而距之。欧曾诸公。亦皆小心不敢杂之于古文。以伤其精约。皆其势固然也。公之兄弟于弱冠时。才气方盛而学识早已成就。声名一日而赫然动天下。然而次公恬静。安于其所成。不思更有进步。惟公明锐之性。如斗之胆。乃于文章。遂生容易心。中年以后。恣意放肆。不复以收敛裁剪为事。且恣意之言。莫快于嬉笑怒骂之时。而言之大者小者横者竖者醇者驳者。并行于一气之中。故他人所弃竹头木屑。在我取用。自与金玉珠贝同功。此其所以皆成文章。可书而诵之者也。茅鹿门录十八罗汉颂云此等文字。韩欧所不欲为。此等见解。韩欧所不能及。有以也夫。
之也。此非其嬉笑怒骂异于人而然也。乃其治文阅历。本自稀有也。自唐以来。古文诸名家。大率积半生工夫。仅能得法于中晚年。故学虽进而才已销。识弥高而气愈衰。但能刊落浮华。以就精约。而不能更有变化于规矩外也。且嬉笑怒骂之言。必出于浮心粗气。而昌黎氏察其不醇。迎而距之。欧曾诸公。亦皆小心不敢杂之于古文。以伤其精约。皆其势固然也。公之兄弟于弱冠时。才气方盛而学识早已成就。声名一日而赫然动天下。然而次公恬静。安于其所成。不思更有进步。惟公明锐之性。如斗之胆。乃于文章。遂生容易心。中年以后。恣意放肆。不复以收敛裁剪为事。且恣意之言。莫快于嬉笑怒骂之时。而言之大者小者横者竖者醇者驳者。并行于一气之中。故他人所弃竹头木屑。在我取用。自与金玉珠贝同功。此其所以皆成文章。可书而诵之者也。茅鹿门录十八罗汉颂云此等文字。韩欧所不欲为。此等见解。韩欧所不能及。有以也夫。读颍滨文
颍滨上韩太尉书。此公十九岁作也。才开口。便说文不可以学而能。即此一言。可见其天资高明。学业已
石菱集卷五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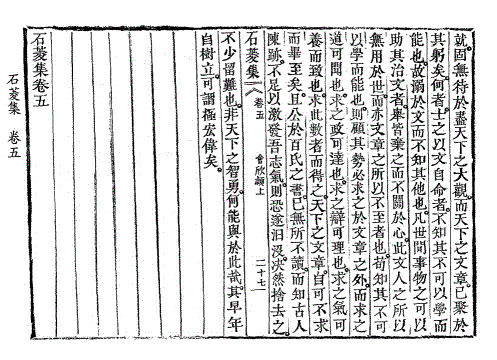 就。固无待于尽天下之大观。而天下之文章。已聚于其躬矣。何者。士之以文自命者。不知其不可以学而能也。故溺于文而不知其他也。凡世间事物之可以助其治文者。举皆弃之而不关于心。此文人之所以无用于世。而亦文章之所以不至者也。苟知其不可以学而能也。则顾其势必求之于文章之外。而求之道可闻也。求之政可达也。求之辩可理也。求之气可养而致也。求此数者而得之。天下之文章。自可不求而毕至矣。且公于百氏之书。已无所不读。而知古人陈迹。不足以激发吾志气。则恐遂汩没。决然舍去之。不少留难也。非天下之智勇。何能与于此哉。其早年自树立。可谓极宏伟矣。
就。固无待于尽天下之大观。而天下之文章。已聚于其躬矣。何者。士之以文自命者。不知其不可以学而能也。故溺于文而不知其他也。凡世间事物之可以助其治文者。举皆弃之而不关于心。此文人之所以无用于世。而亦文章之所以不至者也。苟知其不可以学而能也。则顾其势必求之于文章之外。而求之道可闻也。求之政可达也。求之辩可理也。求之气可养而致也。求此数者而得之。天下之文章。自可不求而毕至矣。且公于百氏之书。已无所不读。而知古人陈迹。不足以激发吾志气。则恐遂汩没。决然舍去之。不少留难也。非天下之智勇。何能与于此哉。其早年自树立。可谓极宏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