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石菱集卷一 第 x 页
石菱集卷一
疏
疏
石菱集卷一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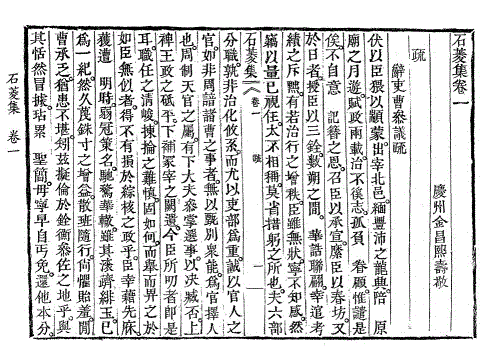 辞吏曹参议疏
辞吏曹参议疏伏以臣猥以颛蒙。出宰北邑。缅丰沛之龙兴。陪 原庙之月游。赋政两载。治不徯志。孤负 眷顾。惟谴是俟。不自意 记簪之恩。召臣以承宣。縻臣以春坊。又于日者。授臣以三铨。数朔之间。 华诰联翩。幸逭考绩之斥黜。有若治行之增秩。臣虽无状。宁不知感。然窃以量己视任。太不相称。莫省措躬之所也。夫六部分职。孰非治化攸系。而尤以吏部为重。诚以官人之官。如非周谙诸曹之事者。无以甄别众能。为官择人也。周制天官之属。有下大夫参掌选事。以决臧否。上裨王政之砥平。下补冢宰之阙遗。今臣所叨者即是耳。职任之清峻。拣抡之难慎。固如何。而举而畀之于如臣无似者。得不有损于综核之政乎。臣幸藉先庥。获遭 明时。弱冠策名。驰骛华辙。虽其滚跻绯玉。已为一纪。然久蔑铢寸之增益。散班随行。尚惧贻羞。閒曹承乏。犹患不堪。矧玆拟伦于铨衡参佐之地乎。与其恬然冒据。玷累 圣简。毋宁早自丐免。还他本分。
石菱集卷一 第 261L 页
 参倚既熟。承趍无望。冒控衷情。干渎 崇听。伏愿 圣明念官方之至重。察臣言之非饰。 特递臣新授吏议之衔。非惟于私为幸。抑亦在公为惬矣。
参倚既熟。承趍无望。冒控衷情。干渎 崇听。伏愿 圣明念官方之至重。察臣言之非饰。 特递臣新授吏议之衔。非惟于私为幸。抑亦在公为惬矣。乞递吏曹参判疏
伏以臣于见职。初不近似。而五年之内。承乏三遭。已试蔑效。愈往侥滥。以臣揆臣。自知既审。顾所以上酬恩造。俯全微谅者。惟在于敛迹荣观。退处冗散。惠徼我天地生成之泽而已。且臣本羸脆。自幼善病。症癖在中。转辗成痼。稍失将摄。辄致冲肆。近因节换。宿祟复发。气滞而神缩。食沮而眩作。人不称职。在所斥退。病有难强。未容迟回。伏乞 圣明曲赐谅察。亟递臣所带铨衔。以幸公私焉。
乞递政府有司堂上疏
伏以皇天眷佑。 国难底定。此诚我 殿下启圣兴邦之会。小大群情。蕲向方切。仍伏念筹司有司之任。揆举 圣允。臣名猥参。愧惧交并。不省所喻。而时值苍黄。趍走是急。黾勉从事。今至匝月馀矣。是岂臣知虑才具有可堪承而然哉。问其职则廊庙吁谟之参赞也。军国机务之与闻也。而顾其人则乃阘茸疏迂。百不犹人。一不攸当者也。自冒忝以来。曾有何发一
石菱集卷一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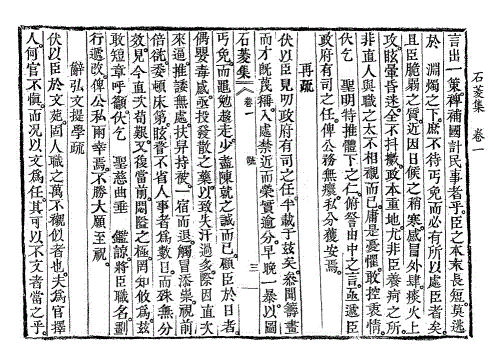 言出一策。裨补国计民事者乎。臣之本末长短。莫逃于 渊烛之下。庶不待丐免而必有所以处臣者矣。且臣脆弱之质。近因日候之稍寒。感冒外肆。痰火上攻。眩晕昏迷。全不抖擞。政本重地。尤非臣养疴之所。非直人与职之太不相衬而已。庸是忧惧。敢控衷情。伏乞 圣明特推体下之仁。俯察由中之言。亟递臣政府有司之任。俾公务无瘝。私分获安焉。
言出一策。裨补国计民事者乎。臣之本末长短。莫逃于 渊烛之下。庶不待丐免而必有所以处臣者矣。且臣脆弱之质。近因日候之稍寒。感冒外肆。痰火上攻。眩晕昏迷。全不抖擞。政本重地。尤非臣养疴之所。非直人与职之太不相衬而已。庸是忧惧。敢控衷情。伏乞 圣明特推体下之仁。俯察由中之言。亟递臣政府有司之任。俾公务无瘝。私分获安焉。乞递政府有司堂上疏[再疏]
伏以臣见叨政府有司之任。半载于玆矣。参闻筹画而才既蔑称。入处禁近而荣实逾分。早晚一暴。以图丐免。而黾勉趍走。少尽陈就之诚而已。顾臣于日者。偶婴毒感。亟投发散之药。以致失汗过多。际因直次来逼。推诿无处。扶舁持被。一宿而退。触冒添祟。视前倍㞃。委顿床第。眩瞀不省人事者为数日。而殊无分效。见今直次苟艰。又复当前。闷隘之极。罔知攸为。玆敢短章呼吁。伏乞 圣慈曲垂 鉴谅。将臣职名。划行递改。俾公私两幸焉。不胜大愿至祝。
辞弘文提学疏
伏以臣于文苑。固人职之万不衬似者也。夫为官择人。何官不慎。而况以文为任。其可以不文者当之乎。
石菱集卷一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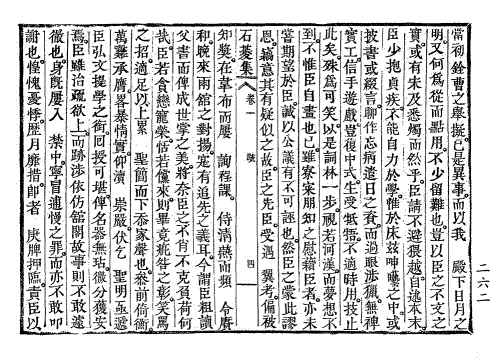 当初铨曹之举拟。已是异事。而以我 殿下日月之明。又何为从而点用。不少留难也。岂以臣之不文之实。或有未及悉烛而然乎。臣请不避猥越。自述本末。臣少抱贞疾。不能自力于学。惟于床玆呻呓之中。或披书或缀言。聊作忘病遣日之资。而过眼涉猎。无裨实工。信手游戏。岂复中式。生受牴牾。不适时用。技止此矣。殊为可笑。以是词林一步。视若河汉。而梦想不到。不惟臣自画也已。虽寮寀朋知之慰藉臣者。亦未尝期望于臣。诚以公议有不可诬也。然臣之蒙此谬恩。窃意其有疑似之故。臣之先臣。受遇 翼考。偏被知奖。在韦布而屡 询程课。 侍清燕而频 令赓和。晚来两馆之对扬。寔有追先之义耳。今谓臣粗读父书而俾成世掌之美。将奈臣之不肖不克负荷何哉。臣若贪恋宠荣。恬若傥来。则毕竟疵咎之彰。笑骂之招。适足以上累 圣简而下忝家声也。参前倚衡。万难承膺。略暴情实。仰渎 崇严。伏乞 圣明亟递臣弘文提学之衔。回授可堪。俾名器无玷。微分获安焉。臣虽治疏欲上。而迹涉依仿馆阁故事则不敢遽彻也。身既屡入 禁中。宁冒逋慢之罪。而亦不敢叩谢也。惶愧忧悸。历月靡措。即者 庚牌押临。责臣以
当初铨曹之举拟。已是异事。而以我 殿下日月之明。又何为从而点用。不少留难也。岂以臣之不文之实。或有未及悉烛而然乎。臣请不避猥越。自述本末。臣少抱贞疾。不能自力于学。惟于床玆呻呓之中。或披书或缀言。聊作忘病遣日之资。而过眼涉猎。无裨实工。信手游戏。岂复中式。生受牴牾。不适时用。技止此矣。殊为可笑。以是词林一步。视若河汉。而梦想不到。不惟臣自画也已。虽寮寀朋知之慰藉臣者。亦未尝期望于臣。诚以公议有不可诬也。然臣之蒙此谬恩。窃意其有疑似之故。臣之先臣。受遇 翼考。偏被知奖。在韦布而屡 询程课。 侍清燕而频 令赓和。晚来两馆之对扬。寔有追先之义耳。今谓臣粗读父书而俾成世掌之美。将奈臣之不肖不克负荷何哉。臣若贪恋宠荣。恬若傥来。则毕竟疵咎之彰。笑骂之招。适足以上累 圣简而下忝家声也。参前倚衡。万难承膺。略暴情实。仰渎 崇严。伏乞 圣明亟递臣弘文提学之衔。回授可堪。俾名器无玷。微分获安焉。臣虽治疏欲上。而迹涉依仿馆阁故事则不敢遽彻也。身既屡入 禁中。宁冒逋慢之罪。而亦不敢叩谢也。惶愧忧悸。历月靡措。即者 庚牌押临。责臣以石菱集卷一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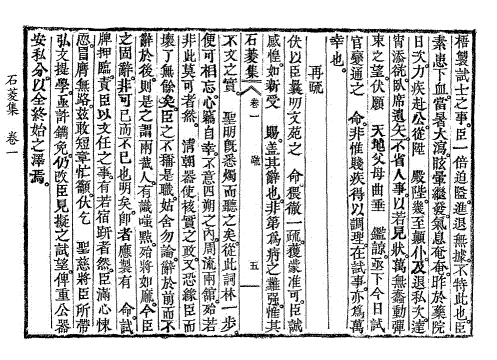 梧制试士之事。臣一倍迫隘。进退无据。不特此也。臣素患下血。当暑大泻。眩晕继发。气息奄奄。昨于药院日次。力疾赴公。从升 殿陛。几至颠仆。及退私次。达宵添㞃。卧席遗矢。不省人事。以若见状。万无蠢动弹束之望。伏愿 天地父母曲垂 鉴谅。亟下今日试官变通之 命。非惟贱疾得以调理。在试事。亦为万幸也。
梧制试士之事。臣一倍迫隘。进退无据。不特此也。臣素患下血。当暑大泻。眩晕继发。气息奄奄。昨于药院日次。力疾赴公。从升 殿陛。几至颠仆。及退私次。达宵添㞃。卧席遗矢。不省人事。以若见状。万无蠢动弹束之望。伏愿 天地父母曲垂 鉴谅。亟下今日试官变通之 命。非惟贱疾得以调理。在试事。亦为万幸也。辞弘文提学疏[再疏]
伏以臣曩叨文苑之 命。猥彻一疏。获蒙准可。臣诚感惶。如新受 赐。盖其辞也。非第为病之难强。惟其不文之实。 圣明既悉烛而听之矣。从此词林一步。便可相忘。心窃自幸。不意四朔之内。周流两馆。殆若非此莫可者然。 清朝器使核实之政。又恐缘臣而坏了无馀矣。臣之不称是职。姑舍勿论。辞于前而不辞于后。则是之谓两截人。有识嗤点。殆将如麻。今臣之固辞。非可已而不已也明矣。即者应制有 命。试牌押临。责臣以文任之事。有若宿趼者然。臣满心悚恧。冒膺无路。玆敢短章忙吁。伏乞 圣慈将臣所带弘文提学。亟许镌免。仍改臣见拟之试望。俾重公器安私分。以全终始之泽焉。
联名自引疏
伏以臣等俱以无似。忝居政府有司之任。一味尸素。丝毫蔑效。蚤夜兢惕。惟谴何是俟。日者府隶作闹。至彻 宸听。而臣等不职之罪尤著矣。苟能常时操饬。稍使畏戢。骇悖之习。岂至于此哉。纲纪隳圮。其咎实在臣等。而及伏见 传教下者。问备薄警。不足以蔽辜。臣等转益惶愧。无地自容。玆敢联声自劾。干冒 威尊。伏乞 圣明亟递臣等见带之衔。仍下臣等司败。更勘未勘之律。以肃邦宪。以安私分焉。
石菱集卷一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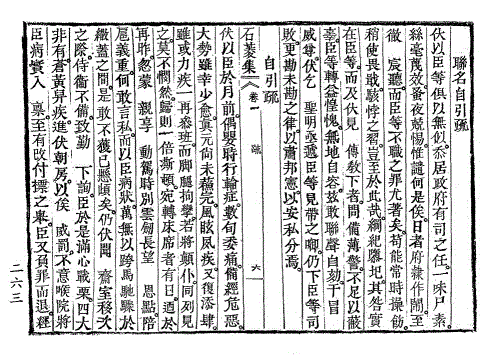 自引疏
自引疏伏以臣于月前。偶婴时行轮症。数旬委痛。备经危恶。大势虽幸少愈。真元尚未苏完。风眩夙疾。又复添肆。虽或力疾一再参班。而脚腿拘挛。若将颠仆。同列见之。莫不悯然。归则一倍凘顿。宛转床席者有日。乃于再昨。忽蒙 亲享 动驾时别云剑长望 恩点。陪扈义重。何敢言私。而以臣病状。万无以跨马驰骤于伞盖之间。是敢不获已悬颐矣。仍伏闻 斋室移次之际。侍卫不备。致勤 下询。臣于是满心战栗。四大非有。苍黄舁疾。进伏朝房。以俟 威罚。不意喉院将臣病实入 禀。至有改付标之举。臣又负罪而退。经
石菱集卷一 第 264H 页
 宵追惟。馀汗浃背。昨伏见 传教下者。以云宝剑事。责饬截严。悬颐人施以重谴之典。而臣名不及焉。臣诚震越駴惑。左右求而不得其说。臣窃妄意或者 圣明以臣舁疾朝房而有所末减欤。是有大不然者。若论悬颐之罪。臣实无别。而罪同罚异。寔有欠于 清朝综核之政矣。且臣独倖逭。情私尤增惶蹙。玆敢短章首实。敢效自劾。伏乞 圣慈谅臣言之寔由衷曲。察臣情之亶出义防。 特下臣司败。亟施当勘之律。俾 朝纲肃而贱分安焉。
宵追惟。馀汗浃背。昨伏见 传教下者。以云宝剑事。责饬截严。悬颐人施以重谴之典。而臣名不及焉。臣诚震越駴惑。左右求而不得其说。臣窃妄意或者 圣明以臣舁疾朝房而有所末减欤。是有大不然者。若论悬颐之罪。臣实无别。而罪同罚异。寔有欠于 清朝综核之政矣。且臣独倖逭。情私尤增惶蹙。玆敢短章首实。敢效自劾。伏乞 圣慈谅臣言之寔由衷曲。察臣情之亶出义防。 特下臣司败。亟施当勘之律。俾 朝纲肃而贱分安焉。石菱集卷一
书
答友人论文书(四首)[其一]
细悉来书。喜闷相半。喜者喜足下之有志古文也。闷者闷足下虽有志而成就无期也。天下万事。无论大小难易。皆不过为当世之事而不借异代。亦惟当世之人如何勾当而已。惟古文之为文。非一世之文。而作者又世不常有。则苟有其人。必非一世之士也。虽其为技枯槁淡薄。上不可以取功名。下不可以得财利。然前人之发愤于此。孜孜一生。不极其工不止者。盖有以见夫生世之事业。惟此为最重。惟此为不朽也。足下生晚海隅。不得亲承作者绪论。而能自有见
石菱集卷一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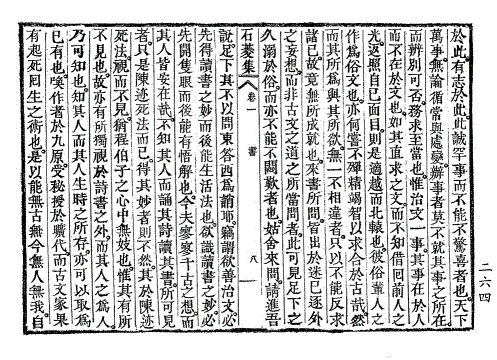 于此。有志于此。此诚罕事而不能不惊喜者也。天下万事。无论循常与处变。办事者莫不就其事之所在。而辨别可否。务求至当也。惟治文一事。其事在于人而不在于文也。如其直求之文。而不知借回前人之光。返照自己面目。则是适越而北辕也。彼俗辈人之作为俗文也。亦何尝不殚精竭智以求合于古哉。然而其所为与其所欲。无一不相违者。只以不能反求诸己。故竟无所成就也。来书所问。皆出于迷己逐外之妄想。而非古文之道之所当问者。此可见足下之久溺于俗。而亦不能不闷叹者也。姑舍来问。请进吾说。足下其不以问东答西为诮耶。窃谓欲善治文。必先得读书之妙而后能生活法也。欲识读书之妙。必先开只眼而后能有悟解也。今夫寥寥千古之想。而其人皆安在哉。不知其人而诵其诗读其书。所可见者。只是陈迹死法而已。得其妙者则不然。其于陈迹死法。视而不见。犹程伯子之心中无妓也。惟其有所不见也。故亦有所独视于诗书之外。而其人之为人。乃可知也。知其人而其人生时之所存。亦可以取为己有也。唤作者于九原。受秘授于旷代。而古文家果有起死回生之术也。是以能无古无今无人无我。自
于此。有志于此。此诚罕事而不能不惊喜者也。天下万事。无论循常与处变。办事者莫不就其事之所在。而辨别可否。务求至当也。惟治文一事。其事在于人而不在于文也。如其直求之文。而不知借回前人之光。返照自己面目。则是适越而北辕也。彼俗辈人之作为俗文也。亦何尝不殚精竭智以求合于古哉。然而其所为与其所欲。无一不相违者。只以不能反求诸己。故竟无所成就也。来书所问。皆出于迷己逐外之妄想。而非古文之道之所当问者。此可见足下之久溺于俗。而亦不能不闷叹者也。姑舍来问。请进吾说。足下其不以问东答西为诮耶。窃谓欲善治文。必先得读书之妙而后能生活法也。欲识读书之妙。必先开只眼而后能有悟解也。今夫寥寥千古之想。而其人皆安在哉。不知其人而诵其诗读其书。所可见者。只是陈迹死法而已。得其妙者则不然。其于陈迹死法。视而不见。犹程伯子之心中无妓也。惟其有所不见也。故亦有所独视于诗书之外。而其人之为人。乃可知也。知其人而其人生时之所存。亦可以取为己有也。唤作者于九原。受秘授于旷代。而古文家果有起死回生之术也。是以能无古无今无人无我。自石菱集卷一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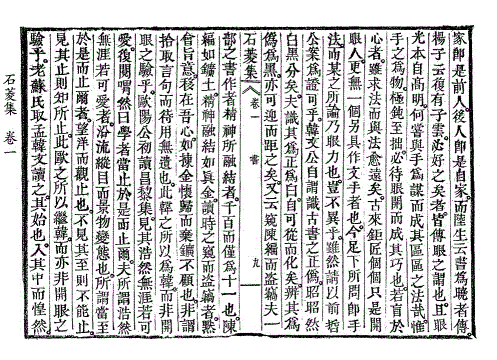 家即是前人。后人即是自家。而陆生云书为晓者传。杨子云复有子云。必好之矣者。皆传眼之谓也。且眼光本自高明。何尝与手为谋而成其区区之法哉。惟手之为物。极钝至拙。必待眼开而成其巧也。若盲于心者。虽求法而与法愈远矣。古来钜匠个个只是开眼人。更无一个另具作文手者也。今足下所问即手法。而某之所论乃眼力也。岂不异乎。虽然请以前哲公案为證可乎。韩文公自谓识古书之正伪。昭昭然白黑分矣。夫识其为正为白。自可从而化矣。辨其为伪为黑。亦可迎而距之矣。又云窥陈编而盗窃夫一部之书作者精神所融结者。千百而仅为十一也。陈编如矿土。精神融结如真金。读时之窥而盗窃者。默会旨意。移在吾心。如拣金怀归而弃矿不顾也。非谓拾取言句而待用无遗也。此韩之所以为韩。而非开眼之验乎。欧阳公初读昌黎集。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复阅喟然曰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夫所谓浩然无涯若可爱者。沿流纵目而景物变态也。所谓当至于是而止尔者。望洋而观止也。不见其至则不能止。见其止则知所止。此欧之所以继韩。而亦非开眼之验乎。老苏氏取孟韩文读之。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
家即是前人。后人即是自家。而陆生云书为晓者传。杨子云复有子云。必好之矣者。皆传眼之谓也。且眼光本自高明。何尝与手为谋而成其区区之法哉。惟手之为物。极钝至拙。必待眼开而成其巧也。若盲于心者。虽求法而与法愈远矣。古来钜匠个个只是开眼人。更无一个另具作文手者也。今足下所问即手法。而某之所论乃眼力也。岂不异乎。虽然请以前哲公案为證可乎。韩文公自谓识古书之正伪。昭昭然白黑分矣。夫识其为正为白。自可从而化矣。辨其为伪为黑。亦可迎而距之矣。又云窥陈编而盗窃夫一部之书作者精神所融结者。千百而仅为十一也。陈编如矿土。精神融结如真金。读时之窥而盗窃者。默会旨意。移在吾心。如拣金怀归而弃矿不顾也。非谓拾取言句而待用无遗也。此韩之所以为韩。而非开眼之验乎。欧阳公初读昌黎集。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复阅喟然曰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夫所谓浩然无涯若可爱者。沿流纵目而景物变态也。所谓当至于是而止尔者。望洋而观止也。不见其至则不能止。见其止则知所止。此欧之所以继韩。而亦非开眼之验乎。老苏氏取孟韩文读之。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石菱集卷一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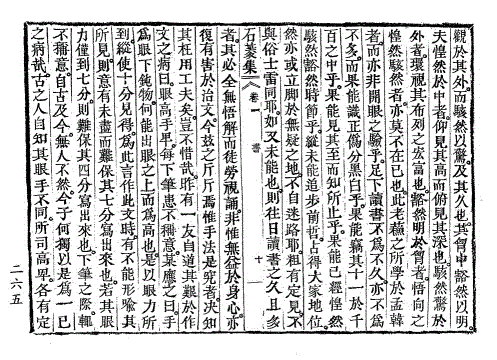 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其胸中豁然以明。夫惶然于中者。仰见其高而俯见其深也。骇然惊于外者。环视其布列之宏富也。豁然明于胸者。悟向之惶然骇然者。亦莫不在己也。此老苏之所学于孟韩者。而亦非开眼之验乎。足下读书不为不久。亦不为不多。而果能识正伪分黑白乎。果能窃其十一于千百之中乎。果能见其至而知所止乎。果能已经惶然骇然豁然时节乎。纵未能追步前哲。占得大家地位。然亦或立脚于无疑之地。不自迷路耶。粗有定见。不与俗士雷同耶。如又未能也。则往日读书之久且多者。其必全无悟解而徒劳视诵。非惟无益于身心。亦复有害于治文。今玆之斤斤焉惟手法是究者。决知其枉用工夫矣。岂不惜哉。昨有一友自道其艰于作文之病曰。眼高手卑。每下笔患不称意。某应之曰。手为眼下钝物。何能出眼之上而为高也。是以眼力所到。纵使十分见得。为此言作此文时。有不能形喻其所见。则意有未尽而难保其七分写出来也。若其眼力仅到七分。则难保其四分写出来也。下笔之际。辄不称意。自古及今。无人不然。今子何独以是为一己之病哉。古之人自知其眼手不同。所司高卑。各有定
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其胸中豁然以明。夫惶然于中者。仰见其高而俯见其深也。骇然惊于外者。环视其布列之宏富也。豁然明于胸者。悟向之惶然骇然者。亦莫不在己也。此老苏之所学于孟韩者。而亦非开眼之验乎。足下读书不为不久。亦不为不多。而果能识正伪分黑白乎。果能窃其十一于千百之中乎。果能见其至而知所止乎。果能已经惶然骇然豁然时节乎。纵未能追步前哲。占得大家地位。然亦或立脚于无疑之地。不自迷路耶。粗有定见。不与俗士雷同耶。如又未能也。则往日读书之久且多者。其必全无悟解而徒劳视诵。非惟无益于身心。亦复有害于治文。今玆之斤斤焉惟手法是究者。决知其枉用工夫矣。岂不惜哉。昨有一友自道其艰于作文之病曰。眼高手卑。每下笔患不称意。某应之曰。手为眼下钝物。何能出眼之上而为高也。是以眼力所到。纵使十分见得。为此言作此文时。有不能形喻其所见。则意有未尽而难保其七分写出来也。若其眼力仅到七分。则难保其四分写出来也。下笔之际。辄不称意。自古及今。无人不然。今子何独以是为一己之病哉。古之人自知其眼手不同。所司高卑。各有定石菱集卷一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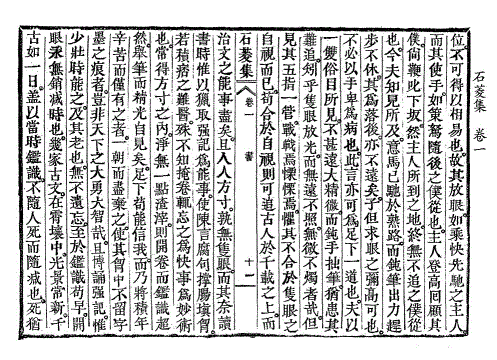 位。不可得以相易也。故其放眼。如乘快先驰之主人。而其使手。如策驽随后之仆从也。主人登高回顾其仆。尚鞭叱下坂。然主人所到之地。终无不追之仆从也。今夫知见所及。意马已驰于熟路。而钝笔出力赶步不休。其为落后。亦不远矣。子但求眼之弥高可也。不必以手卑为病也。此言亦可为足下一道也。夫以一双俗目所见。不甚远大精微。而钝手拙笔。犹患其难追。矧乎只眼放光。而无远不照。无微不烛者哉。但见其五指一管。战战焉慄慄焉。惧其不合于只眼之自视而已。苟合于自视则可追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治文之能事尽矣。且人人方寸。孰无只眼。而其奈读书时惟以猎取强记为能事。使陈言腐句撑肠填胸。若积痞之难医。殊不知掩卷辄忘之为快事为妙术也。常得方寸之内。净无一点渣滓。则开卷而鉴识超然。举笔而精光自见矣。足下苟能信我。而乃将积年辛苦而仅有之者。一朝而尽弃之。使其胸中不留字墨之痕者。岂非天下之大勇大智哉。且博诵强记。惟少壮时能之。及其老也。无不遗忘。至于鉴识苟早。开眼永无销减时也。几家古文。在霄壤中。光景常新。千古如一日。盖以当时鉴识。不随人死而随减也。死犹
位。不可得以相易也。故其放眼。如乘快先驰之主人。而其使手。如策驽随后之仆从也。主人登高回顾其仆。尚鞭叱下坂。然主人所到之地。终无不追之仆从也。今夫知见所及。意马已驰于熟路。而钝笔出力赶步不休。其为落后。亦不远矣。子但求眼之弥高可也。不必以手卑为病也。此言亦可为足下一道也。夫以一双俗目所见。不甚远大精微。而钝手拙笔。犹患其难追。矧乎只眼放光。而无远不照。无微不烛者哉。但见其五指一管。战战焉慄慄焉。惧其不合于只眼之自视而已。苟合于自视则可追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治文之能事尽矣。且人人方寸。孰无只眼。而其奈读书时惟以猎取强记为能事。使陈言腐句撑肠填胸。若积痞之难医。殊不知掩卷辄忘之为快事为妙术也。常得方寸之内。净无一点渣滓。则开卷而鉴识超然。举笔而精光自见矣。足下苟能信我。而乃将积年辛苦而仅有之者。一朝而尽弃之。使其胸中不留字墨之痕者。岂非天下之大勇大智哉。且博诵强记。惟少壮时能之。及其老也。无不遗忘。至于鉴识苟早。开眼永无销减时也。几家古文。在霄壤中。光景常新。千古如一日。盖以当时鉴识。不随人死而随减也。死犹石菱集卷一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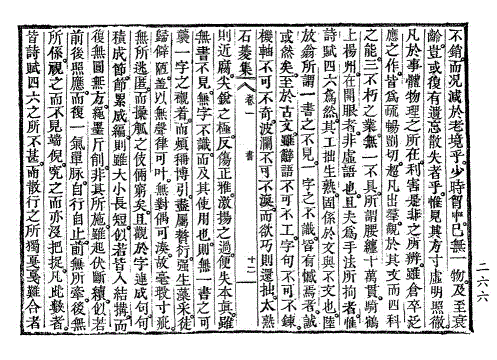 不销。而况减于老境乎。少时胸中。已无一物。及至衰龄。岂或复有遗忘散失者乎。惟见其方寸虚明照彻。凡于事体物理之所在。利害是非之所辨。虽仓卒泛应之作。皆为疏畅剀切。超凡出群。观于其文而四科之能。三不朽之业。无一不具。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杨州。在开眼者。非虚语也。且夫为手法所拘者。惟诗赋四六为然。其工拙生熟。固系于文与不文也。陆放翁所谓一书之不见。一字之不识。皆有憾焉者。诚或然矣。至于古文。虽辞语不可不工。字句不可不鍊。机轴不可不奇。波澜不可不涣。而欲巧则还拙。太熟则近腐。尖锐之极。反伤正雅。激扬之过。便失本真。虽无书不见。无字不识。而及其使用也。则无一书之可袭一字之衬着。而烦称博引。尽属赘衍。强生藻采。徒归僻陋。盖以无声律可叶。无对偶可凑。故毫瑕寸疵。无所逃匿。而操觚之伎俩穷矣。且观于字连成句。句积成节。节累成编。则虽大小长短。似若皆入结搆。而复无圆无方。绳墨斤削。非其所施。虽起伏断续。似若前后照应。而复一气单脉。自行自止。前无所牵。后无所系。视之而不见端倪。究之而亦没把捉。凡此数者。皆诗赋四六之所不甚。而散行之所独戛戛难合者
不销。而况减于老境乎。少时胸中。已无一物。及至衰龄。岂或复有遗忘散失者乎。惟见其方寸虚明照彻。凡于事体物理之所在。利害是非之所辨。虽仓卒泛应之作。皆为疏畅剀切。超凡出群。观于其文而四科之能。三不朽之业。无一不具。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杨州。在开眼者。非虚语也。且夫为手法所拘者。惟诗赋四六为然。其工拙生熟。固系于文与不文也。陆放翁所谓一书之不见。一字之不识。皆有憾焉者。诚或然矣。至于古文。虽辞语不可不工。字句不可不鍊。机轴不可不奇。波澜不可不涣。而欲巧则还拙。太熟则近腐。尖锐之极。反伤正雅。激扬之过。便失本真。虽无书不见。无字不识。而及其使用也。则无一书之可袭一字之衬着。而烦称博引。尽属赘衍。强生藻采。徒归僻陋。盖以无声律可叶。无对偶可凑。故毫瑕寸疵。无所逃匿。而操觚之伎俩穷矣。且观于字连成句。句积成节。节累成编。则虽大小长短。似若皆入结搆。而复无圆无方。绳墨斤削。非其所施。虽起伏断续。似若前后照应。而复一气单脉。自行自止。前无所牵。后无所系。视之而不见端倪。究之而亦没把捉。凡此数者。皆诗赋四六之所不甚。而散行之所独戛戛难合者石菱集卷一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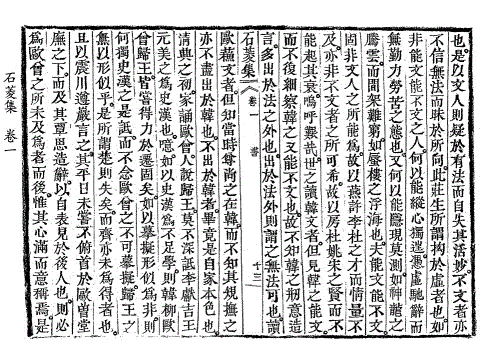 也。是以文人则疑于有法而自失其活妙。不文者亦不信无法而昧于所向。此庄生所谓拘于虚者也。如非能文能不文之人。何以能纵心独𨓏。凭虚驰辞而无勤力劳苦之态也。又何以能隐现莫测。如神龙之腾云。而间架难穷。如蜃楼之浮海也。夫能文能不文。固非文人之所能为。故以燕许李杜之才而情量不及。亦非不文者之所可希。故以房杜姚宋之贤而不能起其衰。呜呼艰哉。世之读韩文者。但见韩之能文。而不复细察韩之又能不文也。故不知韩之刱意造言。多出于法之外也。出于法外则谓之无法可也。读欧苏文者。但知当时尊尚之在韩。而不知其规抚之亦不尽出于韩也。不出于韩者。毕竟是自家本色也。清兴之初。家诵欧曾。人说归王。莫不深诋李献吉王元美之为史汉也。噫。如以史汉为不足学。则韩柳欧曾归王。皆尝得力于迁固矣。如以摹拟形似为非。则何独史汉之是诋。而不念欧曾之不可摹拟。归王之无以形似乎。是所谓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者也。且以震川遵岩言之。其平日未尝不俯首于欧曾堂庑之下。而及其覃思造辞。以自表见于后人也。则必为欧曾之所未及为者而后。惟其心满而意称焉。是
也。是以文人则疑于有法而自失其活妙。不文者亦不信无法而昧于所向。此庄生所谓拘于虚者也。如非能文能不文之人。何以能纵心独𨓏。凭虚驰辞而无勤力劳苦之态也。又何以能隐现莫测。如神龙之腾云。而间架难穷。如蜃楼之浮海也。夫能文能不文。固非文人之所能为。故以燕许李杜之才而情量不及。亦非不文者之所可希。故以房杜姚宋之贤而不能起其衰。呜呼艰哉。世之读韩文者。但见韩之能文。而不复细察韩之又能不文也。故不知韩之刱意造言。多出于法之外也。出于法外则谓之无法可也。读欧苏文者。但知当时尊尚之在韩。而不知其规抚之亦不尽出于韩也。不出于韩者。毕竟是自家本色也。清兴之初。家诵欧曾。人说归王。莫不深诋李献吉王元美之为史汉也。噫。如以史汉为不足学。则韩柳欧曾归王。皆尝得力于迁固矣。如以摹拟形似为非。则何独史汉之是诋。而不念欧曾之不可摹拟。归王之无以形似乎。是所谓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者也。且以震川遵岩言之。其平日未尝不俯首于欧曾堂庑之下。而及其覃思造辞。以自表见于后人也。则必为欧曾之所未及为者而后。惟其心满而意称焉。是石菱集卷一 第 267L 页
 所谓从欧曾入而不从欧曾出者也。夫入据其奥。出破其樊。作者代兴。辄有变改。虽其根基之深厚。有不逮于前人。而规抚精新则往往过之也。叶正则云此事譬如人家觞客。虽或金玉器皿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惟自家罗列者。即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刘桂翁云文章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某谓此二说。虽为操觚家入门正论。然亦为只入外门。未见堂室之奥者也。夫金玉器皿。本非假借之物。设使假借。无不立变为瓷缶瓦杯。而自家之瓷缶瓦杯。久当自化为金玉器皿矣。文章亦器也。器非求旧。惟新而已矣。古文之为古文。以其愈出而愈新也。何不期于新而乃期于古哉。曰善曰不善。在人而不在己。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吾何必较计而取舍哉。古犹不期。而况期于袭乎。善且不期。而况期于同乎。不羡金玉。不耻瓷缶。不期于古。不期于善。惟信在己。刱造日新。千怪万奇。同归浑浩。识此理者。其人品已超然独立于物表。而一切尘容俗状。无由入其笔端矣。足下其试直据胸臆。信笔写出。而叙事叙物。虽欲不为记志得乎。立言尚论。虽欲不为论著得乎。上之告下。虽欲不为诏令得乎。下之告上。虽欲不为
所谓从欧曾入而不从欧曾出者也。夫入据其奥。出破其樊。作者代兴。辄有变改。虽其根基之深厚。有不逮于前人。而规抚精新则往往过之也。叶正则云此事譬如人家觞客。虽或金玉器皿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惟自家罗列者。即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刘桂翁云文章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某谓此二说。虽为操觚家入门正论。然亦为只入外门。未见堂室之奥者也。夫金玉器皿。本非假借之物。设使假借。无不立变为瓷缶瓦杯。而自家之瓷缶瓦杯。久当自化为金玉器皿矣。文章亦器也。器非求旧。惟新而已矣。古文之为古文。以其愈出而愈新也。何不期于新而乃期于古哉。曰善曰不善。在人而不在己。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吾何必较计而取舍哉。古犹不期。而况期于袭乎。善且不期。而况期于同乎。不羡金玉。不耻瓷缶。不期于古。不期于善。惟信在己。刱造日新。千怪万奇。同归浑浩。识此理者。其人品已超然独立于物表。而一切尘容俗状。无由入其笔端矣。足下其试直据胸臆。信笔写出。而叙事叙物。虽欲不为记志得乎。立言尚论。虽欲不为论著得乎。上之告下。虽欲不为诏令得乎。下之告上。虽欲不为石菱集卷一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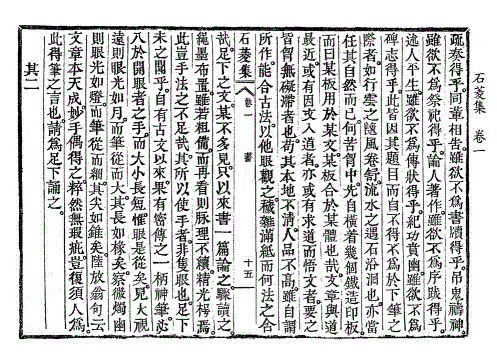 疏奏得乎。同辈相告。虽欲不为书牍得乎。吊鬼祷神。虽欲不为祭祀得乎。论人著作。虽欲不为序跋得乎。述人平生。虽欲不为传状得乎。纪功贲幽。虽欲不为碑志得乎。此皆因其题目而自不得不为于下笔之际者。如行云之随风卷舒。流水之遇石沿洄也。亦当任其自然而已。何苦胸中。先自横着几个铁造印板。而曰某板用于某文。某板合于某体也哉。文章与道最近。或有因文入道者。亦或有求道而悟文者。要之皆胸无碍滞者也。苟其本地不清。人品不高。虽自谓所作。能合古法。以他眼观之。秽杂满纸而何法之合哉。足下之文。某不多见。只以来书一篇论之。骤读之。绳墨布置。虽若粗备。而再看则脉理不续。精光枵焉。此岂手法之不足哉。其所以使手者。非只眼也。足下未之闻乎。自有古文以来。果有密传之一柄神笔。必入于开眼者之手。而大小长短。惟眼是从矣。见大视远则眼光如月。而笔从而大。其长如椽矣。察微烛幽则眼光如灯。而笔从而细。其尖如锥矣。陆放翁句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此得笔之言也。请为足下诵之。
疏奏得乎。同辈相告。虽欲不为书牍得乎。吊鬼祷神。虽欲不为祭祀得乎。论人著作。虽欲不为序跋得乎。述人平生。虽欲不为传状得乎。纪功贲幽。虽欲不为碑志得乎。此皆因其题目而自不得不为于下笔之际者。如行云之随风卷舒。流水之遇石沿洄也。亦当任其自然而已。何苦胸中。先自横着几个铁造印板。而曰某板用于某文。某板合于某体也哉。文章与道最近。或有因文入道者。亦或有求道而悟文者。要之皆胸无碍滞者也。苟其本地不清。人品不高。虽自谓所作。能合古法。以他眼观之。秽杂满纸而何法之合哉。足下之文。某不多见。只以来书一篇论之。骤读之。绳墨布置。虽若粗备。而再看则脉理不续。精光枵焉。此岂手法之不足哉。其所以使手者。非只眼也。足下未之闻乎。自有古文以来。果有密传之一柄神笔。必入于开眼者之手。而大小长短。惟眼是从矣。见大视远则眼光如月。而笔从而大。其长如椽矣。察微烛幽则眼光如灯。而笔从而细。其尖如锥矣。陆放翁句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此得笔之言也。请为足下诵之。答友人论文书[其二]
石菱集卷一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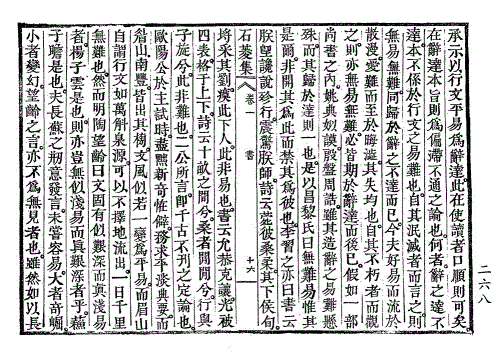 承示以行文平易为辞达。此在使读者口顺则可矣。在辞达本旨则为偏滞不通之论也。何者。辞之达不达。本不系于行文之易难也。自其泯灭者而言之。则无易无难。同归于辞之不达而已。今夫好易而流于散漫。爱难而至于晦涩。其失均也。自其不朽者而观之。则亦无易无难。必皆期于辞达而后已。假如一部尚书之内。姚典姒谟。殷盘周诰。虽其造辞之易难悬殊。而其归于达则一也。是以昌黎氏曰无难易惟其是尔。非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李习之亦曰书云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埒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云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云十亩之间兮。桑者閒閒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二公所言。即千古不刊之定论也。欧阳公于主试时。尽黜新奇怪僻。务求平淡典要。而眉山,南丰。皆出其榜。文风似若一变为平易。而眉山自谓行文如万斛泉源。可以不择地流出。一日千里无难也。然而明陶望龄曰文固有似艰深而真浅易者。杨子云是也。则亦岂无似浅易而真艰深者乎。苏子瞻是也。夫长苏之刱意发言。未尝容易。大者奇崛。小者变幻。望龄之言。亦不为无见者也。虽然如以长
承示以行文平易为辞达。此在使读者口顺则可矣。在辞达本旨则为偏滞不通之论也。何者。辞之达不达。本不系于行文之易难也。自其泯灭者而言之。则无易无难。同归于辞之不达而已。今夫好易而流于散漫。爱难而至于晦涩。其失均也。自其不朽者而观之。则亦无易无难。必皆期于辞达而后已。假如一部尚书之内。姚典姒谟。殷盘周诰。虽其造辞之易难悬殊。而其归于达则一也。是以昌黎氏曰无难易惟其是尔。非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李习之亦曰书云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埒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云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云十亩之间兮。桑者閒閒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二公所言。即千古不刊之定论也。欧阳公于主试时。尽黜新奇怪僻。务求平淡典要。而眉山,南丰。皆出其榜。文风似若一变为平易。而眉山自谓行文如万斛泉源。可以不择地流出。一日千里无难也。然而明陶望龄曰文固有似艰深而真浅易者。杨子云是也。则亦岂无似浅易而真艰深者乎。苏子瞻是也。夫长苏之刱意发言。未尝容易。大者奇崛。小者变幻。望龄之言。亦不为无见者也。虽然如以长石菱集卷一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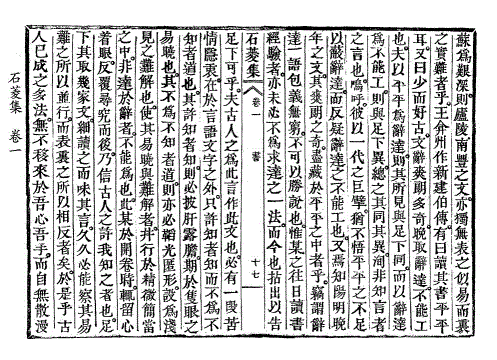 苏为艰深。则庐陵,南丰之文。亦独无表之似易而里之实难者乎。王弇州作新建伯传。有曰读其书平平耳。又曰少而好古。文辞爽朗多奇。晚取辞达。不能工也。夫以平平为辞达。则其所见与足下同。而以辞达为不能工。则与足下异。总之其同其异。洵非知言者之言也。呜呼。彼以一代之巨擘。犹不悟平平之不足以蔽辞达。而反疑辞达之不能工也。又焉知阳明晚年之文。其爽朗之奇。尽藏于平平之中者乎。窃谓辞达一语包义无穷。不可以胜说也。惟某之往日读书经验者。亦未必不为求达之一法。而今也拈出以告足下可乎。夫古人之为此言作此文也。必有一段苦情隐衷。在于言语文字之外。只许知者知而不为不知者道也。其许知者知。则必披肝露胆。期于只眼之易晓也。其不为不知者道。则亦必韬光匿形。设为浅见之难解也。使其易晓与难解者。并行于精微简当之中。非达于辞者。不能为也。此某于开卷时。辄留心着眼。反覆寻究而后。乃信古人之许我知之者也。足下其取几家文。细读之而味其言。久久必能察其易难之所以并行。而表里之所以相反者矣。于是乎古人已成之多法。无不移来于吾心吾手。而自无散漫
苏为艰深。则庐陵,南丰之文。亦独无表之似易而里之实难者乎。王弇州作新建伯传。有曰读其书平平耳。又曰少而好古。文辞爽朗多奇。晚取辞达。不能工也。夫以平平为辞达。则其所见与足下同。而以辞达为不能工。则与足下异。总之其同其异。洵非知言者之言也。呜呼。彼以一代之巨擘。犹不悟平平之不足以蔽辞达。而反疑辞达之不能工也。又焉知阳明晚年之文。其爽朗之奇。尽藏于平平之中者乎。窃谓辞达一语包义无穷。不可以胜说也。惟某之往日读书经验者。亦未必不为求达之一法。而今也拈出以告足下可乎。夫古人之为此言作此文也。必有一段苦情隐衷。在于言语文字之外。只许知者知而不为不知者道也。其许知者知。则必披肝露胆。期于只眼之易晓也。其不为不知者道。则亦必韬光匿形。设为浅见之难解也。使其易晓与难解者。并行于精微简当之中。非达于辞者。不能为也。此某于开卷时。辄留心着眼。反覆寻究而后。乃信古人之许我知之者也。足下其取几家文。细读之而味其言。久久必能察其易难之所以并行。而表里之所以相反者矣。于是乎古人已成之多法。无不移来于吾心吾手。而自无散漫石菱集卷一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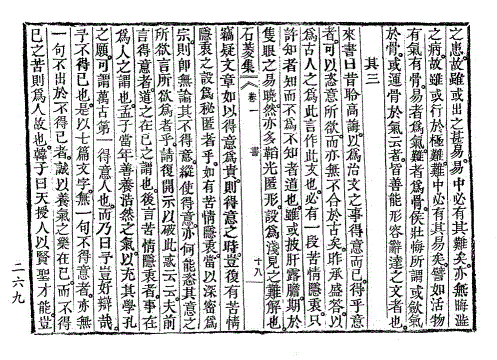 之患。故虽或出之甚易。易中必有其难矣。亦无晦涩之病。故虽或行于极难。难中必有其易矣。譬如活物有气有骨。易者为气。难者为骨。侯壮悔所谓或敛气于骨。或运骨于气云者。皆善能形容辞达之文者也。
之患。故虽或出之甚易。易中必有其难矣。亦无晦涩之病。故虽或行于极难。难中必有其易矣。譬如活物有气有骨。易者为气。难者为骨。侯壮悔所谓或敛气于骨。或运骨于气云者。皆善能形容辞达之文者也。答友人论文书[其三]
来书曰昔聆高诲。以为治文之事得意而已。得乎意者。可以恣意所欲。而亦无不合于古矣。昨承盛答。以为古人之为此言作此文也。必有一段苦情隐衷。只许知者知而不为不知者道也。虽或披肝露胆。期于只眼之易晓。然亦多韬光匿形。设为浅见之难解也。窃疑文章如以得意为贵。则得意之时。岂复有苦情隐衷之设为秘匿者乎。如有苦情隐衷。当以深密为宗。则即无论其不得意。纵使得意。亦何能恣其意之所欲言所欲为者乎。请复开示以破此惑云云。夫前言得意者。道之在己之谓也。后言苦情隐衷者。事在为人之谓也。孟子当年善养浩然之气。以充其学孔之愿。可谓万古第一得意人也。而乃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以七篇文字。无一句不得意者。亦无一句不出于不得已者。诚以养气之乐在己。而不得已之苦则为人故也。韩子曰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
石菱集卷一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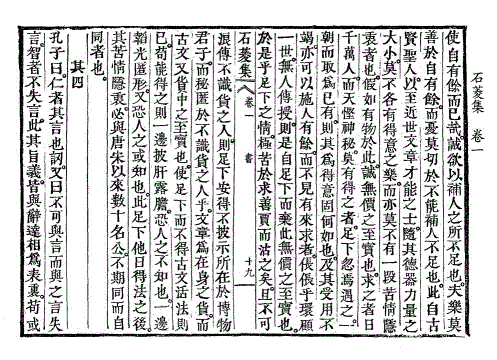 使自有馀而已哉。诚欲以补人之所不足也。夫乐莫善于自有馀。而忧莫切于不能补人不足也。此自古贤圣人。以至近世文章才能之士。随其德器力量之大小。莫不各有得意之乐。而亦莫不有一段苦情隐衷者也。假如有物于此。诚无价之至宝也。求之者日千万人。而天悭神秘。莫有得之者。足下忽焉遇之。一朝而取为己有。则其为得意固何如也。及其受用不竭。亦可以施人有馀。而不见有来求者。伥伥乎环顾一世。无人传授。则是自足下而弃此无价之至宝也。于是乎足下之情。极苦于求善贾而沽之矣。且不可浪传不识货之人。则足下安得不披示所在于博物君子。而秘匿于不识货之人乎。文章为在身之货。而古文又货中之至宝也。使足下而不得古文活法则已。苟能得之则一边披肝露胆。恐人之不知也。一边韬光匿形。又恐人之或知也。此足下他日得法之后。其苦情隐衷。必与唐宋以来数十名公。不期同而自同者也。
使自有馀而已哉。诚欲以补人之所不足也。夫乐莫善于自有馀。而忧莫切于不能补人不足也。此自古贤圣人。以至近世文章才能之士。随其德器力量之大小。莫不各有得意之乐。而亦莫不有一段苦情隐衷者也。假如有物于此。诚无价之至宝也。求之者日千万人。而天悭神秘。莫有得之者。足下忽焉遇之。一朝而取为己有。则其为得意固何如也。及其受用不竭。亦可以施人有馀。而不见有来求者。伥伥乎环顾一世。无人传授。则是自足下而弃此无价之至宝也。于是乎足下之情。极苦于求善贾而沽之矣。且不可浪传不识货之人。则足下安得不披示所在于博物君子。而秘匿于不识货之人乎。文章为在身之货。而古文又货中之至宝也。使足下而不得古文活法则已。苟能得之则一边披肝露胆。恐人之不知也。一边韬光匿形。又恐人之或知也。此足下他日得法之后。其苦情隐衷。必与唐宋以来数十名公。不期同而自同者也。答友人论文书[其四]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又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言。此其旨义。皆与辞达相为表里。苟或
石菱集卷一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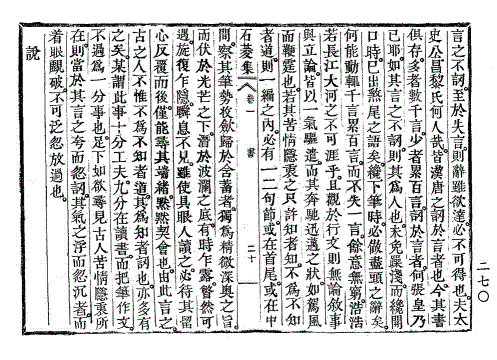 言之不讱。至于失言。则辞虽欲达。必不可得也。夫太史公,昌黎氏何人哉。皆汉唐之讱于言者也。今其书俱存。多者数千言。少者累百言。讱于言者。何张皇乃已耶。如其言之不讱。则其为人也。未免躁浅。而才开口时。已出煞尾之语矣。才下笔时。必做尽头之辞矣。何能动辄千言累百言。而不失一言。馀意无穷。浩浩若长江大河之不可涯乎。且观于行文则无论叙事与立论。皆以一气驱遣。而其奔驰迅迈之状。如驾风而鞭霆也。若其苦情隐衷之只许知者知。不为不知者道。则一编之内。必有一二句节。或在首尾。或在中间。察其笔势收敛归于含蓄者。独为精微深奥之旨。而伏于光芒之下。潜于波澜之底。有时乍露。瞥然可遇。旋复乍隐。瞬息不见。虽使具眼人读之。必待其留心反覆而后。仅能寻其端绪。默默契会也。由此言之。古之人不惟不为不知者道。其为知者讱也。亦多有之矣。某谓此事十分工夫。九分在读书。而把笔作文。不过为一分事也。足下如欲寻见古人苦情隐衷所在。则当于其言之夸而忽讱。其气之浮而忽沉者。而着眼觑破。不可泛忽放过也。
言之不讱。至于失言。则辞虽欲达。必不可得也。夫太史公,昌黎氏何人哉。皆汉唐之讱于言者也。今其书俱存。多者数千言。少者累百言。讱于言者。何张皇乃已耶。如其言之不讱。则其为人也。未免躁浅。而才开口时。已出煞尾之语矣。才下笔时。必做尽头之辞矣。何能动辄千言累百言。而不失一言。馀意无穷。浩浩若长江大河之不可涯乎。且观于行文则无论叙事与立论。皆以一气驱遣。而其奔驰迅迈之状。如驾风而鞭霆也。若其苦情隐衷之只许知者知。不为不知者道。则一编之内。必有一二句节。或在首尾。或在中间。察其笔势收敛归于含蓄者。独为精微深奥之旨。而伏于光芒之下。潜于波澜之底。有时乍露。瞥然可遇。旋复乍隐。瞬息不见。虽使具眼人读之。必待其留心反覆而后。仅能寻其端绪。默默契会也。由此言之。古之人不惟不为不知者道。其为知者讱也。亦多有之矣。某谓此事十分工夫。九分在读书。而把笔作文。不过为一分事也。足下如欲寻见古人苦情隐衷所在。则当于其言之夸而忽讱。其气之浮而忽沉者。而着眼觑破。不可泛忽放过也。石菱集卷一
说
石菱集卷一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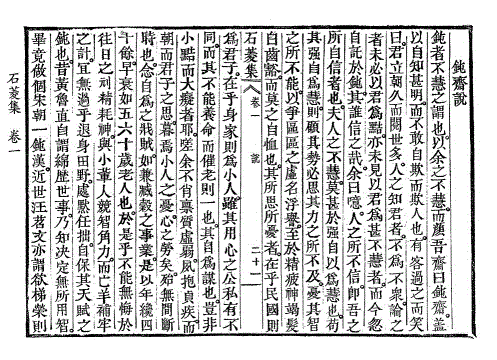 钝斋说
钝斋说钝者不慧之谓也。以余之不慧。而颜吾斋曰钝斋。盖以自知甚明。而不敢自欺而欺人也。有客过之而笑曰。君立朝久而阅世多。人之知君者。不为不众。论之者未必以君为黠。亦未见以君为甚不慧者。而今忽自托于钝。其谁信之哉。余曰噫。人之所不信。即吾之所自信者也。夫人之不慧。莫甚于强自以为慧也。苟其强自为慧。则顾其势必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以争区区之虚名浮誉。至于精疲神竭发白齿豁。而莫之自恤也。其所思所忧者。在乎民国则为君子。在乎身家则为小人。虽其用心之公私有不同。而其不能养命而催老则一也。其自为谋也。岂非小黠而大痴者耶。嗟余不肖禀质虚弱。夙抱贞疾。而朝而君子之思。暮焉小人之忧。心之劳矣。殆无间断时也。念自为之戕贼。如兼臧谷之事业。是以年才四十馀。早衰如五六十岁老人也。于是乎不能无悔于往日之刓精耗神。与小辈人竞智角力。而亡羊补牢之计。宜无过乎退身田野。处默任拙。自保其天赋之钝也。昔黄鲁直自谓绵历世事。乃知决定无所用智。毕竟做个宋朝一钝汉。近世汪苕文亦谓欲梯荣则
石菱集卷一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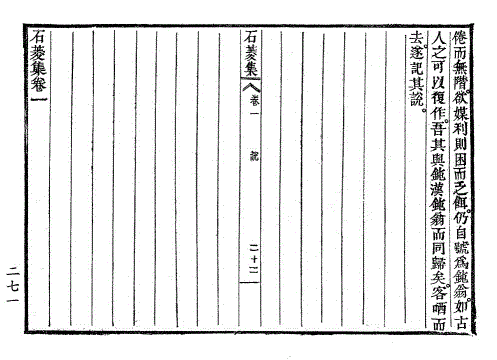 倦而无阶。欲媒利则困而乏饵。仍自号为钝翁。如古人之可以复作。吾其与钝汉钝翁而同归矣。客哂而去。遂记其说。
倦而无阶。欲媒利则困而乏饵。仍自号为钝翁。如古人之可以复作。吾其与钝汉钝翁而同归矣。客哂而去。遂记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