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杂著○论语记疑
杂著○论语记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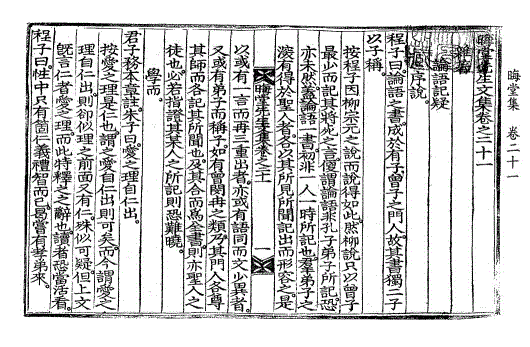 序说。
序说。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按程子因柳宗元之说而说得如此。然柳说只以曾子最少而记其将死之言。便谓论语非孔子弟子所记。恐亦未然。盖论语一书。初非一人一时所记也。群弟子之深有得于圣人者。各以其所见所闻记出而形容之。是以或有一言而再三重出者。亦或有语同而文少异者。又或有弟子而称子。如有曾闵冉之类。乃其门人各尊其师而各记其所闻也。及其合而为全书。则亦圣人之徒也。必若指證其某人之所记则恐难晓。
学而。
君子务本章注。朱子曰。爱之理自仁出。
按爱之理是仁也。谓之爱自仁出则可矣。而今谓爱之理自仁出。则却似理之前面又有仁。殊似可疑。但上文既言仁者爱之理。而此特释之之辞也。读者恐当活看。
程子曰。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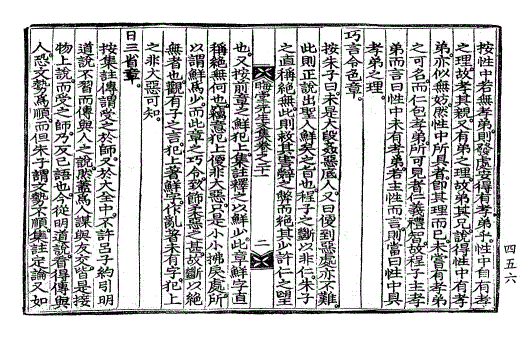 按性中若无孝弟。则发处安得有孝弟乎。性中自有孝之理。故孝其亲。又有弟之理。故弟其兄。说得性中有孝弟。亦似无妨。然性中所具者。即其理而已。未尝有孝弟之可名。而仁包孝弟。所可见者仁义礼智。故程子主孝弟而言曰性中未有孝弟。若主性而言。则当曰性中具孝弟之理。
按性中若无孝弟。则发处安得有孝弟乎。性中自有孝之理。故孝其亲。又有弟之理。故弟其兄。说得性中有孝弟。亦似无妨。然性中所具者。即其理而已。未尝有孝弟之可名。而仁包孝弟。所可见者仁义礼智。故程子主孝弟而言曰性中未有孝弟。若主性而言。则当曰性中具孝弟之理。巧言令色章。
按朱子曰。未是大段奸恶底人。又曰便到恶处亦不难。此则正说出圣人鲜矣之旨也。程子之断以非仁。朱子之直称绝无。此则救其害辞之弊而绝其少许仁之望也。又按前章之鲜犯上。集注释之以鲜少。此章鲜字直称绝无何也。窃意犯上便非大恶。只是小小拂戾处。所以谓鲜为少。而此章之巧令。致饰柔恶之甚。故断以绝无者也。观有子之言。犯上著鲜字。作乱著未有字。犯上之非大恶可知。
日三省章。
按集注传谓受之于师。又于大全中。不许吕子约引明道说不习而传与人之说。然盖为人谋与友交。皆是接物上说。而受之师。乃反己语也。今从明道说。看得传与人。恐文势为顺。而但朱子谓文势不顺。集注定论又如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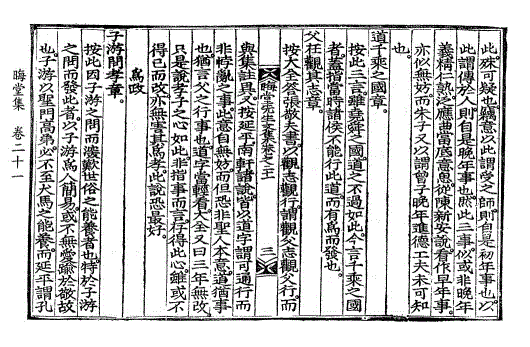 此。殊可疑也。窃意以此谓受之师。则自是初年事也。以此谓传于人。则自是晚年事也。然此三事。似或非晚年义精仁熟。泛应曲当底意思。从陈新安说。看作早年事。亦似无妨。而朱子又以谓曾子晚年进德工夫。未可知也。
此。殊可疑也。窃意以此谓受之师。则自是初年事也。以此谓传于人。则自是晚年事也。然此三事。似或非晚年义精仁熟。泛应曲当底意思。从陈新安说。看作早年事。亦似无妨。而朱子又以谓曾子晚年进德工夫。未可知也。道千乘之国章。
按此三言。虽尧舜之国。道之不过如此。今言千乘之国者。盖指当时诸侯不能行此道。而有为而发也。
父在观其志章。
按大全答张敬夫书。以观志观行。谓观父志观父行。而与集注异。又按延平,南轩诸说。皆以道字谓可通行而非悖乱之事。此意自无妨。而但恐非圣人本意。道犹事也。犹言父之行事也。道字当轻看。大全又曰三年无改。只是说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存得此心。虽或不得已而改。亦无害其为孝。此说恐最好。
为政
子游问孝章。
按此因子游之问而深叹世俗之能养者也。特于子游之问而发此者。以子游为人简易。或不无爱踰于敬故也。子游以圣门高弟。必不至犬马之能养。而延平谓孔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7L 页
 门学者亦未免如此。此养亲者之所当深戒也。
门学者亦未免如此。此养亲者之所当深戒也。终日不违章。问不违与耳顺相近否。朱子曰。不违是颜子于孔子说话。都晓得。耳顺是无所不通。
按孔颜地位虽不同。而但不违及耳顺。似是一般地头矣。盖颜子于孔子之言。不违而无不通。则触物触事。莫不皆然。是不亦耳顺乎。所谓耳顺者。亦只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则颜子之不违。似亦无异于此矣。然但颜子之于圣人之言。虽其心融意会。而或不免思而得。所以不及耳顺地头耶。
温故知新章。
按温故知新。自是学者事。而何以言为人师也。语意似不相当。殊可疑也。窃意有人只以记闻之学。无知新之益。而其病在好为人师。故夫子诫之如此。讥其人之不足为人师也。伊川尝谓只此一事可师。盖谓此事可师。非人能此即可师。朱子以谓于文义未安。
先行其言章。
按行之于未言之前则集注说当矣。言之于既行之后则集注说可疑。盖既行之后。何事可言。且从字似有行底意。而集注直解作言字。尤所可疑。窃意夫子之意以谓先其言而行其所可言者。后其言而从其所已言者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8H 页
 也。盖子贡多言。故诫之以此。
也。盖子贡多言。故诫之以此。攻乎异端章。
按异端所当攻击者也。攻之而何害之有哉。此攻字不当作攻击之攻明矣。大全始以攻击之攻言之。而觉其未安。集注训以专治。證之以攻金攻玉之攻。犹言汉儒所谓专门之治也。盖孔子之时。初无异端。杨墨之说未著。佛氏之教不入。虽有老子而孔子为之问礼。则在当时。又非异端之著见者也。然则所谓异端。特非圣人之教。而如百家众技之流。便可去略理会而不可专治者也。专治而欲精之。反不免骎骎于其中。不亦害乎。或曰苟如此矣。集注谓如杨墨是也。则杨墨之学。虽不可以专治。亦可以略理会否。曰虽杨墨之学。先自略理会。然后可知其是非得失之归而知所以拒之矣。特先专治其学。欲察其归而精之。则将骎骎于无父无君矣。或曰然则朱子曰略去理会他不得。又何也。曰初学者只可自治而已。虽略理会。便自不可。而若是我有定见。亦可以理会之矣。所以朱子旋又曰自家学有定止。去看他却得也。朱子于此章。屡变其说。而集注说始为定论。然苟不善读。亦有可疑。读者宜致思焉。
八佾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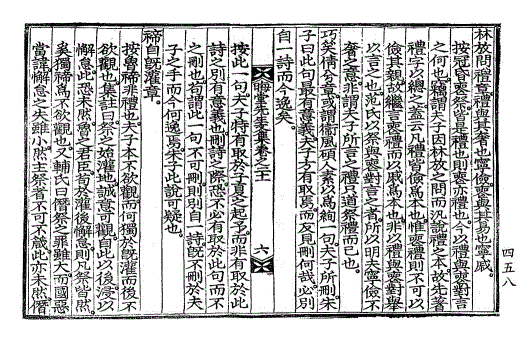 林放问礼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问礼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按冠昏丧祭。皆是礼也则丧亦礼也。今以礼与丧对言之何也。窃谓夫子因林放之问而汎说礼之本。故先著礼字以总之。盖云凡礼皆俭为本也。惟丧礼则不可以俭其亲。故继言丧礼而以戚为本也。非以礼与丧对举以言之也。范氏以祭与丧对言之者。所以明夫宁俭不奢之意。非谓夫子所言之礼只道祭礼而已也。
巧笑倩兮章。或谓卫风硕人素以为绚一句。夫子所删。朱子曰此句最有意义。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见删何哉。必别自一诗而今逸矣。
按此一句。夫子特有取于子夏之起予。而非有取于此诗之别有意义也。删诗之际。恐不必有取于此句而不之删也。苟谓此一句不可删。则别自一诗。既不删于夫子之手而今何逸焉。朱子此说可疑也。
禘自既灌章。
按鲁禘非礼也。夫子本不欲观。而何独于既灌而后不欲观也。集注曰。祭之始灌地。诚意可观。自此以后。浸以懈怠。此恐未然。鲁之君臣。苟于灌后懈怠。则凡祭皆然。奚独禘为不欲观也。又辅氏曰僭祭之罪虽大。而国恶当讳。懈怠之失虽小。然主祭者不可不箴。此亦未然。僭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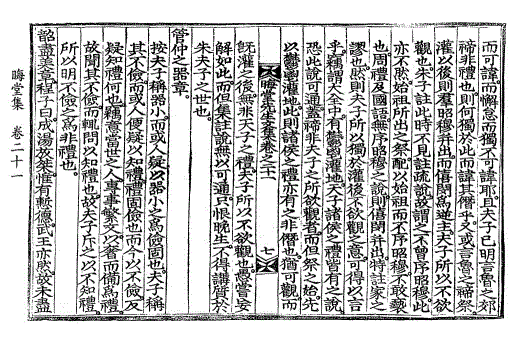 而可讳。而懈怠而独不可讳耶。且夫子已明言鲁之郊禘非礼也。则何独于此而讳其僭乎。又或言鲁之禘祭。灌以后则群昭穆并出。而僖闵为逆主。夫子所以不欲观也。朱子注此时不见注疏说。故谓之不曾序昭穆。此亦不然。始祖所出之祭。配以始祖而不序昭穆。不敢亵也。周礼及国语。无序昭穆之说。则僖闵并出。特注家之谬也。然则夫子所以独于灌后不欲观之意。可得以言乎。窃谓大全中。有郁鬯灌地。天子诸侯之礼皆有之说。恐此说可通。盖禘非夫子之所欲观者。而但祭之始。先以郁鬯灌地。此则诸侯之礼亦有之非僭也。犹可观。而既灌之后。无非天子之礼。夫子所以不欲观也。愚尝妄解如此。而但集注说无以可通。只恨晚生。不得讲质于朱夫子之世也。
而可讳。而懈怠而独不可讳耶。且夫子已明言鲁之郊禘非礼也。则何独于此而讳其僭乎。又或言鲁之禘祭。灌以后则群昭穆并出。而僖闵为逆主。夫子所以不欲观也。朱子注此时不见注疏说。故谓之不曾序昭穆。此亦不然。始祖所出之祭。配以始祖而不序昭穆。不敢亵也。周礼及国语。无序昭穆之说。则僖闵并出。特注家之谬也。然则夫子所以独于灌后不欲观之意。可得以言乎。窃谓大全中。有郁鬯灌地。天子诸侯之礼皆有之说。恐此说可通。盖禘非夫子之所欲观者。而但祭之始。先以郁鬯灌地。此则诸侯之礼亦有之非僭也。犹可观。而既灌之后。无非天子之礼。夫子所以不欲观也。愚尝妄解如此。而但集注说无以可通。只恨晚生。不得讲质于朱夫子之世也。管仲之器章。
按夫子称器小。而或人疑以器小之为俭固也。夫子称其不俭。而或人便疑以知礼。礼固俭也而今以不俭。反疑知礼何也。窃意当世之人。专事繁文。以奢而备为礼。故闻其不俭。而辄问以知礼也。故夫子斥之以不知礼。所以明不俭之为非礼也。
韶尽美章。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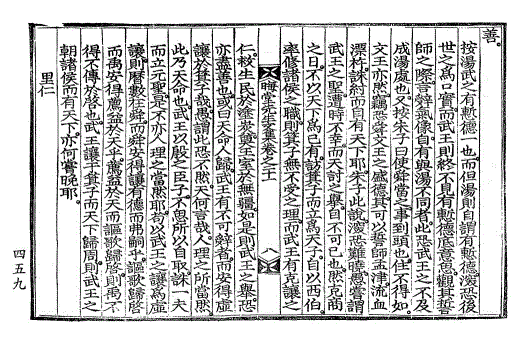 善。
善。按汤武之有惭德一也。而但汤则自谓有惭德。深恐后世之为口实。而武王则终不见有惭德底意思。观其誓师之际。言辞气像。自有与汤不同者。此恐武王之不及成汤处也。又按朱子曰使舜当之。事到头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窃恐舜文王之盛德。其可以誓师孟津。流血漂杵。诛纣而自有天下耶。朱子此说。深恐难晓。愚尝谓武王之圣。遭时不幸。而天讨之举。自不可已也。然克商之日。不以天下为己有。访箕子而立为天子。自以西伯。率修诸侯之职。则箕子无不受之理。而武王有克让之仁。救生民于涂炭。奠王室于无疆。如是则武王之举。恐亦尽善也。或曰天命人归。武王有不可辞者。而安得虚让于箕子哉。愚谓此恐不然。天何言哉。人理之所当然。此乃天命也。武王以殷之臣子。不思所以自取。诛一夫而立元圣。是不亦人理之当然耶。苟以武王之让为虚让。则历数在舜。而舜安得让有德而弗嗣乎。讴歌归启而禹安得荐益于天乎。荐益于天而讴歌归启。则禹不得不传于启也。武王让于箕子而天下归周。则武王之朝诸侯而有天下。亦何尝晚耶。
里仁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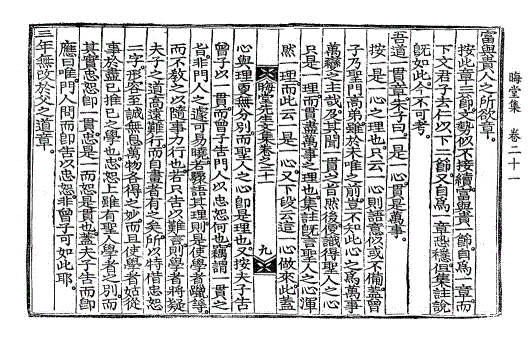 富与贵人之所欲章。
富与贵人之所欲章。按此章三节。文势似不接续。富与贵一节。自为一章。而下文君子去仁以下二节。又自为一章恐稳。但集注说既如此。今不可考。
吾道一贯章。朱子曰。一是一心。贯是万事。
按一是一心之理也。只云一心则语意似或不备。盖曾子乃圣门高弟。虽于未唯之前。岂不知此心之为万事万变之主哉。及其闻一贯之旨然后。便识得圣人之心只是一理。而贯尽万事之理也。集注既言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此云一是一心。又下段云这一心做来。此盖心与理更无分别。而圣人之心即是理也。又按夫子告曾子以一贯。而曾子告门人以忠恕何也。窃谓一贯之旨。非门人之遽可易晓。若骤语其理。则是使学者躐等。而不教之以随事力行也。若只告以难言。则学者将疑夫子之道高远难行。而自画者有之矣。所以特借忠恕二字。形容至诚无息万物各得之妙。而且使学者姑从事于尽己推己之学也。忠恕上虽有圣人学者之别。而其实忠恕即一贯。忠是一而恕是贯也。盖夫子告而即应曰唯。门人问而即告以忠恕。非曾子可如此耶。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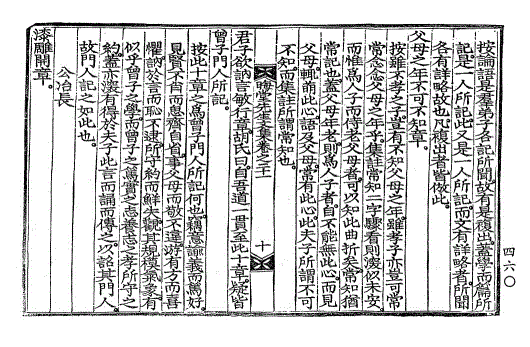 按论语是群弟子各记所闻。故有是复出。盖学而篇所记。是一人所记。此又是一人所记。而文有详略者。所闻各有详略故也。凡复出者皆仿此。
按论语是群弟子各记所闻。故有是复出。盖学而篇所记。是一人所记。此又是一人所记。而文有详略者。所闻各有详略故也。凡复出者皆仿此。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章。
按虽不孝之子。岂有不知父母之年。虽孝子亦岂可常常念念父母之年乎。集注常知二字骤看则深似未安。而惟为人子而侍老父母者。可以知此曲折矣。常知犹常记也。盖父母年老。则为人子者。自不能无此心。而见父母。辄萌此心。语及父母。常有此心。此夫子所谓不可不知。而集注所谓常知也。
君子欲讷言敏行章。胡氏曰。自吾道一贯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门人所记。
按此十章之为曾子门人所记何也。窃意谕义而笃好。见贤不肖而思齐自省。事父母而敬不违。游有方而喜惧。讷于言而耻不逮。所守约而鲜失。观其规模气象。有似乎曾子之学。而曾子之笃实之志养志之孝所守之约。盖亦深有得于夫子此言而诵而传之。以诏其门人。故门人记之如此也。
公冶长
漆雕开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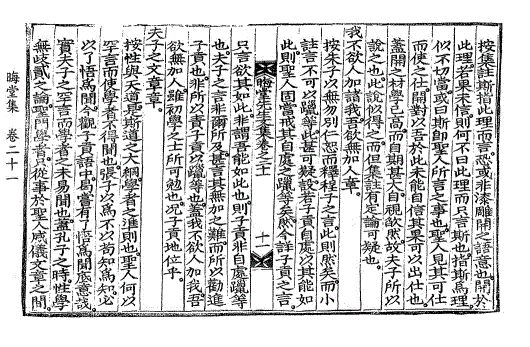 按集注斯指此理而言。恐或非漆雕开之语意也。开于此理。若果未信。则何不曰此理而只言斯也。指斯为理。似不切当。或曰斯即圣人所言之事也。圣人见其可仕而使之仕。开对以吾于此未能自信其果可以出仕也。盖开之材学已高。而自期甚大。自视欿然。故夫子所以说之也。此说似得之。而但集注有定论可疑也。
按集注斯指此理而言。恐或非漆雕开之语意也。开于此理。若果未信。则何不曰此理而只言斯也。指斯为理。似不切当。或曰斯即圣人所言之事也。圣人见其可仕而使之仕。开对以吾于此未能自信其果可以出仕也。盖开之材学已高。而自期甚大。自视欿然。故夫子所以说之也。此说似得之。而但集注有定论可疑也。我不欲人加诸我。吾欲无加人章。
按朱子以无勿别仁恕而释程子之言。此则然矣。而小注言不可以躐等。此甚可疑。设若子贡自处以其能如此。则圣人固当戒其自处之躐等矣。然今详子贡之言。只言欲其如此。非谓吾能如此也。则子贡非自处躐等也。夫子之言非尔所及。甚言其无加之难。而所以劝进子贡也。非所以责子贡以躐等也。盖我不欲人加我。吾欲无加人。虽初学之士所可勉也。况子贡地位乎。
夫子之文章章。
按性与天道。是斯道之大纲。学者之准则也。圣人何以罕言而使学者不得闻也。张子以为不以苟知为知。必以了悟为闻。今观子贡语中。曷尝有了悟为闻底意哉。实夫子之罕言而学者之未易闻也。盖孔子之时。性学无歧贰之论。圣门学者。只从事于圣人威仪文章之间。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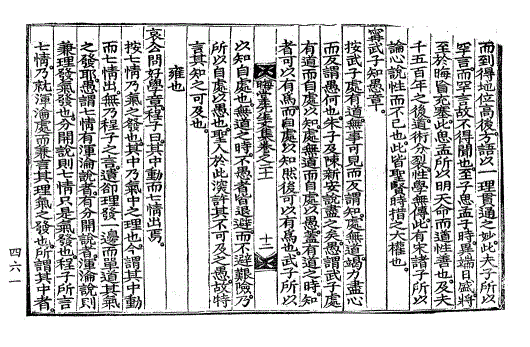 而到得地位高后。方语以一理贯通之妙。此夫子所以罕言。而罕言故不得闻也。至子思孟子时。异端日盛。将至于晦盲充塞。此思孟所以明天命而道性善也。及夫千五百年之后。道术分裂。性学无传。此有宋诸子所以论心说性而不已也。此皆圣贤时措之大权也。
而到得地位高后。方语以一理贯通之妙。此夫子所以罕言。而罕言故不得闻也。至子思孟子时。异端日盛。将至于晦盲充塞。此思孟所以明天命而道性善也。及夫千五百年之后。道术分裂。性学无传。此有宋诸子所以论心说性而不已也。此皆圣贤时措之大权也。宁武子知愚章。
按武子处有道。无事可见而反谓知。处无道。竭力尽心而反谓愚何也。朱子及陈新安说尽之矣。愚谓武子处有道而自处以知。处无道而自处以愚。盖有道之时。知者可以有为。而自处以知然后可以有为也。武子所以以知自处也。无道之时。不愚者皆退避。而不避艰险。乃所以自处以愚也。圣人于此深许其不可及之愚。故特言其知之可及也。
雍也
哀公问好学章。程子曰。其中动而七情出焉。
按七情乃气之发也。其中乃气中之理也。今谓其中动而七情出。无乃程子之言。遗却理发一边而单道其气之发耶。愚谓七情有浑沦说者。有分开说者。浑沦说则兼理发气发也。分开说则七情只是气发也。程子所言七情。乃就浑沦处而兼言其理气之发也。所谓其中者。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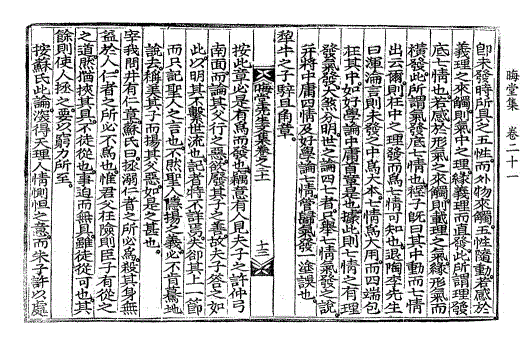 即未发时所具之五性。而外物来触。五性随动。若感于义理之来触。则气中之理。缘义理而直发。此所谓理发底七情也。若感于形气之来触。则载理之气。缘形气而横发。此所谓气发底七情也。程子既曰其中动而七情出云尔。则在中之理发而为七情可知也。退陶李先生曰浑沦言则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而四端包在其中。如好学论中庸首章是也。据此则七情之有理发气发。大煞分明。世之论四七者。只举七情气发之说。并将中庸四情及好学论七情。管归气发一涂误也。
即未发时所具之五性。而外物来触。五性随动。若感于义理之来触。则气中之理。缘义理而直发。此所谓理发底七情也。若感于形气之来触。则载理之气。缘形气而横发。此所谓气发底七情也。程子既曰其中动而七情出云尔。则在中之理发而为七情可知也。退陶李先生曰浑沦言则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而四端包在其中。如好学论中庸首章是也。据此则七情之有理发气发。大煞分明。世之论四七者。只举七情气发之说。并将中庸四情及好学论七情。管归气发一涂误也。犁牛之子骍且角章。
按此章必是有为而发也。窃意有人见夫子之许仲弓南面。而论其父行之恶。欲废其子之善。故夫子答之如此。以明其不系世流也。记者特不详焉。失却其上一节而只记圣人之言也。不然圣人隐扬之义。必不肯蓦地说去。称美其子而扬其父恶。如是之甚也。
宰我问井有仁章。苏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为。杀其身无益于人。仁者之所必不为也。惟君父在险则臣子有从之之道。然犹挟其具。不徒从也。事迫而无具。虽徒从可也。其馀则使人拯之。要以穷力所至。
按苏氏此论。深得天理人情恻怛之意。而朱子许以处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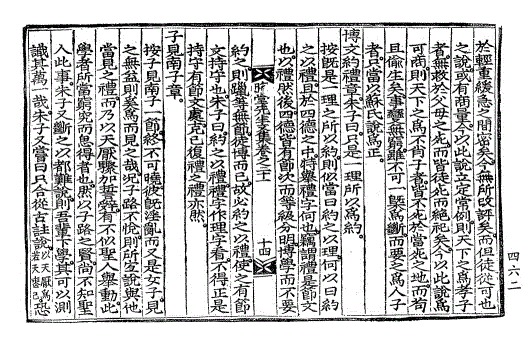 于轻重缓急之间密矣。今无所改评矣。而但徒从可也之说。或有商量。今以此说立定常例。则天下之为孝子者。无救于父母之死。而皆徒死而绝祀矣。今以此说为可商。则天下之为不肖子者。皆不死于当死之地。而苟且偷生矣。事变无穷。虽不可一槩为断。而要之为人子者。只当以苏氏说为正。
于轻重缓急之间密矣。今无所改评矣。而但徒从可也之说。或有商量。今以此说立定常例。则天下之为孝子者。无救于父母之死。而皆徒死而绝祀矣。今以此说为可商。则天下之为不肖子者。皆不死于当死之地。而苟且偷生矣。事变无穷。虽不可一槩为断。而要之为人子者。只当以苏氏说为正。博文约礼章。朱子曰。只是一理所以为约。
按既是一理之所以约。则似当曰约之以理。何以曰约之以礼。且于四德之中。特举礼字何也。窃谓礼是节文也。以礼然后。四德皆有节次而等级分明。博学而不要约之。则躐等无节。徒博而已。故必约之以礼。使之有节文持守也。朱子曰。约之以礼。礼字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节文处。克己复礼之礼亦然。
子见南子章。
按子见南子一节。终不可晓。彼既淫乱而又是女子。见之无益则奚为而见之哉。况子路不悦。则所宜说与他当见之礼。而乃以天厌骤加誓辞。有不似圣人举动。此学者所当穷究而思得者也。然以子路之贤。尚不知圣人此事。朱子又断之以都难说。则吾辈下学。其可以测识其万一哉。朱子又尝曰只合从古注说。(以天厌为若天丧己。)恐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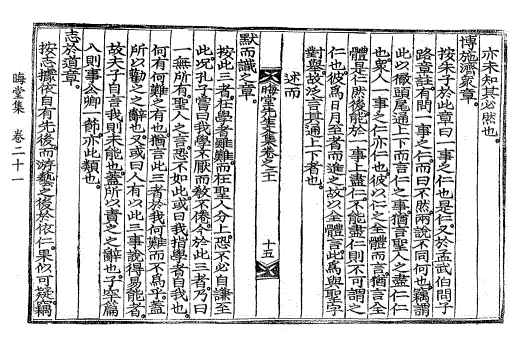 亦未知其必然也。
亦未知其必然也。博施济众章。
按朱子于此章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又于孟武伯问子路章注。有问一事之仁。而曰不然。两说不同何也。窃谓此以彻头尾通上下而言仁之事。犹言圣人之尽仁仁也。众人一事之仁亦仁也。彼以仁之全体而言。犹言全体是仁然后。能于一事上尽仁。不能尽仁则不可谓之仁也。彼为日月至者而进之。故以全体言。此为与圣字对举。故泛言其通上下者也。
述而
默而识之章。
按此三者。在学者虽难。而在圣人分上。恐不必自谦至此。况孔子尝曰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今于此三者。乃曰一无所有。圣人之言。恐不如此。或曰我指学者自我也。何有何难之有也。犹言此三者于我何难而不为乎。盖所以劝之之辞也。又或曰人有以此三事说得易能者。故夫子自言我则未能也。盖所以责之之辞也。子罕篇入则事公卿一节。亦此类也。
志于道章。
按志据依自有先后。而游艺之后于依仁。果似可疑。窃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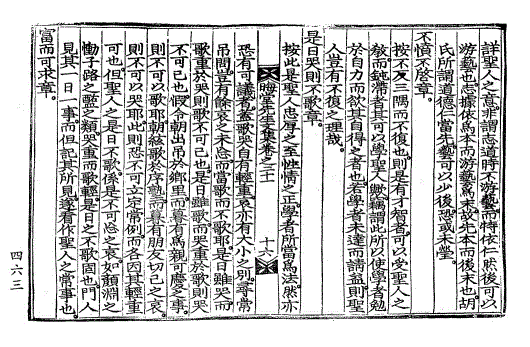 详圣人之意。非谓志道时不游艺。而特依仁然后可以游艺也。志据依为本而游艺为末。故先本而后末也。胡氏所谓道德仁当先。艺可以少后。恐或未莹。
详圣人之意。非谓志道时不游艺。而特依仁然后可以游艺也。志据依为本而游艺为末。故先本而后末也。胡氏所谓道德仁当先。艺可以少后。恐或未莹。不愤不启章。
按不反三隅而不复也。则是有才智者。可以受圣人之教。而钝滞者其可以学圣人欤。窃谓此所以使学者勉于自力而欲其自得之者也。若学者未达而请益。则圣人岂有不复之理哉。
是日哭则不歌章。
按此是圣人忠厚之至性情之正。学者所当为法。然亦恐有可议者。盖歌哭自有轻重。哀亦有大小之别。寻常吊问。岂有馀哀之未忘。而当歌而不歌耶。是日虽哭。而歌重于哭则歌不可已也。是日虽歌。而哭重于歌则哭不可已也。假令朝出吊于乡里。而暮有为亲可庆之事。则不可以歌耶。朝弦歌于序塾。而暮有朋友切己之哀。则不可以哭耶。此则恐不可立定常例。而各因其轻重可也。但圣人之是日不歌。系是不可忘之哀。如颜渊之恸子路之醢之类。哭重而歌轻。是日之不歌固也。门人见其一日一事。而但记其所见。遂看作圣人之常事也。
富而可求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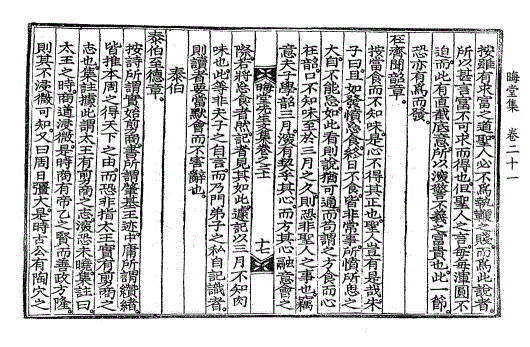 按虽有求富之道。圣人必不为执鞭之贱。而为此说者。所以甚言富不可求而得也。但圣人之言。每每浑圆不迫。而此有直截底意。所以深警不义之富贵也。此一节。恐亦有为而发。
按虽有求富之道。圣人必不为执鞭之贱。而为此说者。所以甚言富不可求而得也。但圣人之言。每每浑圆不迫。而此有直截底意。所以深警不义之富贵也。此一节。恐亦有为而发。在齐闻韶章。
按当食而不知味。是心不得其正也。圣人岂有是哉。朱子曰。且如发愤忘食。终日不食。皆非常事。所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如此看则说犹可通。而苟谓之方食而心在韶。口不知味。至于三月之久。则恐非圣人之事也。窃意夫子学韶三月。深有契乎其心。而方其心融意会之际。若将忘食者然。记者见其如此。遽记以三月不知肉味也。此等非夫子之自言。而乃门弟子之私自记识者。则读者要当默会而不害辞也。
泰伯
泰伯至德章。
按诗所谓实始剪商。书所谓肇基王迹。中庸所谓缵绪。皆推本周之得天下之由。而恐非指太王实有剪商之志也。集注据此谓太王有剪商之志。深恐未晓。集注曰。太王之时。商道浸微。是时商有帝乙之贤而善政方隆。则其不浸微可知。又曰周日彊大。是时古公有陶穴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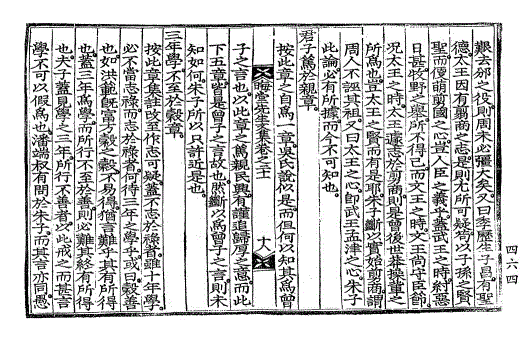 艰去邠之役。则周未必彊大矣。又曰季历生子昌。有圣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是则尤所可疑。苟以子孙之贤圣。而便萌剪国之心。岂人臣之义乎。盖武王之时。纣恶日甚。牧野之举。所不得已。而文王之时。文王尚守臣节。况太王之时。太王遽志于剪商。则是曾后世莽操辈之所为也。岂太王之贤而有是耶。朱子断以实始剪商。谓周人不诬其祖。又曰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朱子此论。必有所据。而今不可知也。
艰去邠之役。则周未必彊大矣。又曰季历生子昌。有圣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是则尤所可疑。苟以子孙之贤圣。而便萌剪国之心。岂人臣之义乎。盖武王之时。纣恶日甚。牧野之举。所不得已。而文王之时。文王尚守臣节。况太王之时。太王遽志于剪商。则是曾后世莽操辈之所为也。岂太王之贤而有是耶。朱子断以实始剪商。谓周人不诬其祖。又曰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朱子此论。必有所据。而今不可知也。君子笃于亲章。
按此章之自为一章。吴氏说似是。而但何以知其为曾子之言也。以此章之笃亲民兴。有谨追归厚之意。而此下五章。皆是曾子之言故也。然断以为曾子之言。则未知如何。朱子所以只许近是也。
三年学。不至于谷章。
按此章集注改至作志可疑。盖不志于禄者。虽十年学。必不当志禄。而志于禄者。何待三年之学乎。或曰。谷善也。如洪范既富方谷之谷。不易得。犹言难乎其有所得也。盖三年为学。而所行不至于善。则必难其终有所得也。夫子盖见学之三年。所行不善者。以此戒之而甚言学不可以假为也。潘端叔有问于朱子。而其言亦同。愚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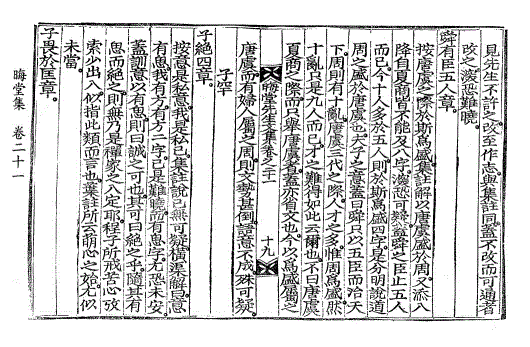 见先生不许之。改至作志。与集注同。盖不改而可通者改之。深恐难晓。
见先生不许之。改至作志。与集注同。盖不改而可通者改之。深恐难晓。舜有臣五人章。
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集注解以唐虞盛于周。又添入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八字。深恐可疑。盖舜之臣止五人而已。今十人多于五人。则于斯为盛四字。是分明说道周之盛于唐虞也。夫子之意盖曰舜只以五臣而治天下。周则有十乱。唐虞三代之际。人才之多。惟周为盛。然十乱只是九人而已。才之难得如此云尔也。不曰唐虞夏商之际。而只举唐虞者。盖亦省文也。今以为盛属之唐虞。而有妇人属之周。则文势甚倒。语意不成。殊可疑。
子罕
子绝四章。
按意是私意。我是私己。集注说已无可疑。横渠解曰。意有思。我有方。有方二字。已是难晓。而有思字。尤恐未安。盖训意以有思。则曰诚之可也。其可曰绝之乎。随其有思而绝之。则无乃是禅家之入定耶。程子所戒苦心考索少出入。似指此类而言也。叶注所云萌心之始。尤似未当。
子畏于匡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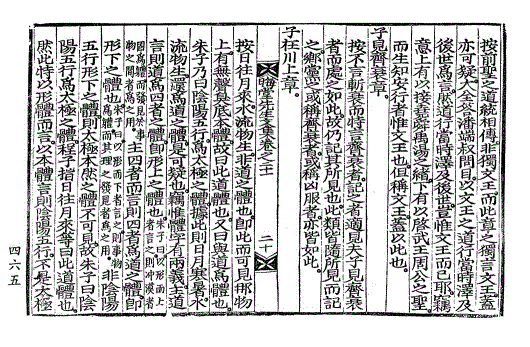 按前圣之道统相传。非独文王。而此章之独言文王。盖亦可疑。大全答潘端叔问目。以文王之道行当时泽及后世为言。然道行当时泽及后世。岂惟文王而已耶。窃意上有以接尧舜禹汤之绪。下有以启武王周公之圣。而生知安行者惟文王也。但称文王。盖以此也。
按前圣之道统相传。非独文王。而此章之独言文王。盖亦可疑。大全答潘端叔问目。以文王之道行当时泽及后世为言。然道行当时泽及后世。岂惟文王而已耶。窃意上有以接尧舜禹汤之绪。下有以启武王周公之圣。而生知安行者惟文王也。但称文王。盖以此也。子见齐衰章。
按不言斩衰而特言齐衰者。记之者适见夫子见齐衰者而处之如此。故仍记其所见也。此类皆随所见而记之。乡党之或称齐衰者。或称凶服者。亦皆如此。
子在川上章。
按日往月来。水流物生。非道之体也。即此而可见那物上。有无声臭底本体。故曰此道体也。又曰与道为体也。朱子乃曰阴阳五行。为太极之体。据此则日月寒暑。水流物生。还为道之体。是可疑也。窃惟体字有两义。主道言则道为四者之体。即形上之体也。(朱子曰。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发见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主四者而言则四者为道之体。即形下之体也。(朱子曰。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非阴阳五行形下之体。则太极本然之体不可见。故朱子曰阴阳五行为太极之体。程子指日往月来等曰此道体也。然此特以形体而言。以本体言则阴阳五行。不是太极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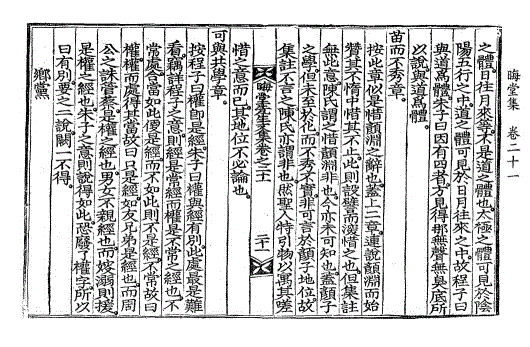 之体。日往月来等。不是道之体也。太极之体可见于阴阳五行之中。道之体可见于日月往来之中。故程子曰与道为体。朱子曰因有四者。方见得那无声无臭底所以说。与道为体。
之体。日往月来等。不是道之体也。太极之体可见于阴阳五行之中。道之体可见于日月往来之中。故程子曰与道为体。朱子曰因有四者。方见得那无声无臭底所以说。与道为体。苗而不秀章。
按此章似是惜颜渊之辞也。盖上二章。连说颜渊而始赞其不惰中惜其不止。此则设譬而深惜之也。但集注无此意。陈氏谓之惜颜渊非也。今亦未可知也。盖颜子之学。但未至于化。而不秀不实。非可言于颜子地位。故集注不言之。陈氏亦谓非也。然圣人特引物以寓其嗟惜之意而已。其地位不必论也。
可与共学章。
按程子曰权即是经。朱子曰权与经有别。此处最是难看。窃详程子之意。则经是常经而权是不常之经也。不常处。合当如此便是经。而不如此则不是经。不常故曰权。权而处得其当故曰只是经。如友兄弟是经也。而周公之诛管蔡。是权之经也。男女不亲经也。而嫂溺则援。是权之经也。朱子之意则说得如此。恐废了权字。所以曰有别。要之二说。阙一不得。
乡党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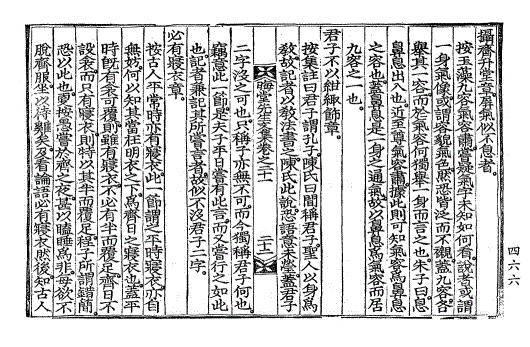 摄齐升堂章。屏气似不息者。
摄齐升堂章。屏气似不息者。按玉藻九容气容肃。尝疑气字未知如何看。说者或谓一身气像。或谓容貌气色。然恐皆泛而不衬。盖九容。各举其一容。而于气容何独举一身而言之也。朱子曰。息鼻息出入也。近至尊气容肃。据此则可知气容为鼻息之容也。盖鼻息是一身之通气。故以鼻息为气容而居九容之一也。
君子不以绀緅饰章。
按集注曰君子谓孔子。陈氏曰间称君子。圣人以身为教。故记者以教法书之。陈氏此说。恐语意未莹。盖君子二字没之可也。只称子亦无不可。而今独称君子何也。窃意此一节。是夫子平日尝有此言。而又尝行之如此也。记者兼记其所尝言者。故似不没君子二字。
必有寝衣章。
按古人平常时亦有寝衣。此一节谓之平时寝衣。亦自无妨。何以知其当在明衣之下。为齐日之寝衣也。盖平时既有衾可覆。则虽有寝衣。不必有半而覆足。齐日不设衾。而只有寝衣。则特以其半而覆足。程子所谓错简。恐以此也。更按愚尝于齐之夜。甚以瞌睡为非。每欲不脱齐服。坐以待鸡矣。及看论语必有寝衣然后。知古人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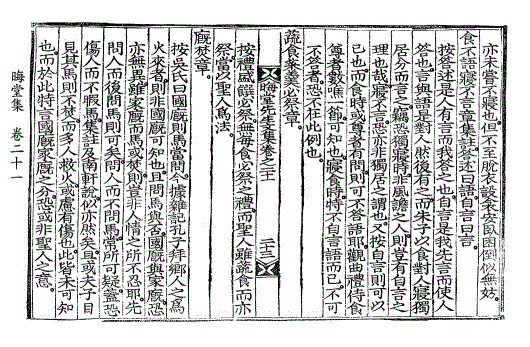 亦未尝不寝也。但不至脱衣设衾安卧困倒似无妨。
亦未尝不寝也。但不至脱衣设衾安卧困倒似无妨。食不语寝不言章集注。答述曰语。自言曰言。
按答述是人有言而我答之也。自言是我先言而使人答也。言与语是对人然后有之。而朱子以食对人寝独居分而言之。窃恐独寝时。非风谵之人。则岂有自言之理也哉。寝不言。恐亦非独居之谓也。又按自言则可以已也。而食时或尊者有问。则可不答语耶。观曲礼侍食尊者数噍一节。可知也。寝食时。特不自言语而已。不可不答者。恐不在此例也。
蔬食菜羹必祭章。
按礼盛馔必祭。无每食必祭之礼。而圣人虽蔬食而亦祭。当以圣人为法。
厩焚章。
按吴氏曰国厩则马当问。今据杂记孔子拜乡人之为火来者。则非国厩可知也。且问马与否。国厩与家厩。恐亦无异。虽家厩而马或焚。则岂非人情之所不忍耶。先问人而后问马则可矣。问人而不问马。常所可疑。盖恐伤人而不暇马。集注及南轩说。似亦然矣。且或夫子目见其马则不焚。而多人救火。或虑有伤也。此皆未可知也。而于此特言国厩家厩之分。恐或非圣人之意。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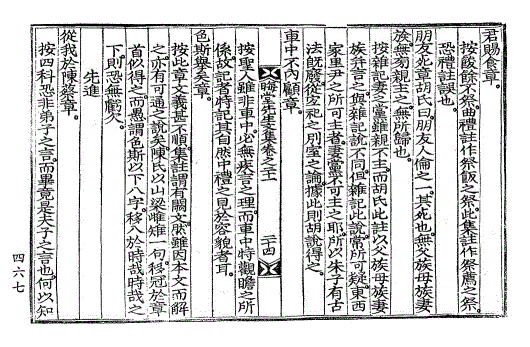 君赐食章。
君赐食章。按馂馀不祭。曲礼注作祭饭之祭。此集注作祭荐之祭。恐礼注误也。
朋友死章胡氏曰。朋友人伦之一。其死也。无父族母族妻族。无旁亲主之。无所归也。
按杂记妻之党虽亲不主。而胡氏此注以父族母族妻族并言之。与杂记说不同。但杂记此说。常所可疑。东西家里尹之所可主者。妻党不可主之耶。所以朱子有古法既废。从宜祀之别室之论。据此则胡说得之。
车中不内顾章。
按圣人虽非车中。必无疾言之理。而车中特观瞻之所系。故记者特记其自然中礼之见于容貌者耳。
色斯举矣章。
按此章文义甚不顺。集注谓有阙文。然虽因本文而解之。亦有可通之说矣。陈氏以山梁雌雉一句。移冠于章首似得之。而愚谓色斯以下八字。移入于时哉时哉之下。则恐无亏欠。
先进
从我于陈蔡章。
按四科恐非弟子之言。而毕竟是夫子之言也。何以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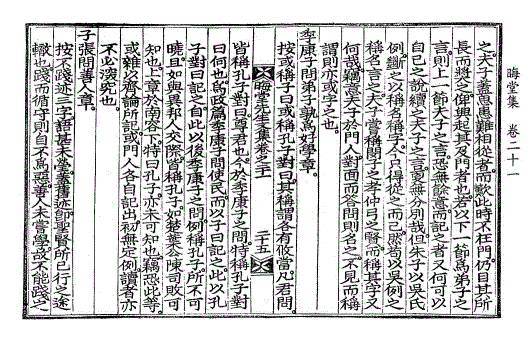 之。夫子盖思患难相从者。而叹此时不在门。仍目其所长而奖之。俾兴起其及门者也。若以下一节为弟子之言。则上一节夫子之言。恐无馀意。而记之者又何可以自己之说续之夫子之言。更无分别哉。但朱子以吴氏例。断之以称名称字。今只得从之而已。然苟以吴例之称名言之。夫子尝称闵子之孝仲弓之贤。而称其字又何哉。窃意夫子于门人。对面而答问则名之。不见而称谓则亦或字之也。
之。夫子盖思患难相从者。而叹此时不在门。仍目其所长而奖之。俾兴起其及门者也。若以下一节为弟子之言。则上一节夫子之言。恐无馀意。而记之者又何可以自己之说续之夫子之言。更无分别哉。但朱子以吴氏例。断之以称名称字。今只得从之而已。然苟以吴例之称名言之。夫子尝称闵子之孝仲弓之贤。而称其字又何哉。窃意夫子于门人。对面而答问则名之。不见而称谓则亦或字之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章。
按或称子曰或称孔子对曰。其称谓各有攸当。凡君问。皆称孔子对曰。尊君也。今于季康子之问。特称孔子对曰何也。为政篇季康子问使民。而以子曰记之。此以孔子对曰记之。自此以后季康子之问。例称孔子。所不可晓。且如与异邦人交际。皆称孔子。如楚叶公陈司败可知也。上章于南容下。特曰孔子。亦未可知也。窃恐此等。或杂以齐论所记。或门人各自记出。初无定例。读者亦不必深究也。
子张问善人章。
按不践迹三字。语甚未莹。盖旧迹。即圣贤所已行之途辙也。践而循守则自不为恶。善人未尝学。故不能践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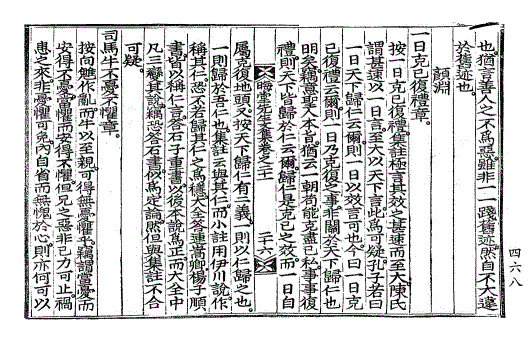 也。犹言善人之不为恶。虽非一一践旧迹。然自不大违于旧迹也。
也。犹言善人之不为恶。虽非一一践旧迹。然自不大违于旧迹也。颜渊
一日克己复礼章。
按一日克己复礼。集注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陈氏谓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此为可疑。孔子若曰一日天下归仁云尔。则一日以效言可也。今曰一日克己复礼云尔。则一日乃克复之事。非关于天下归仁也明矣。窃意圣人本旨。犹云一朝苟能克尽己私。事事复礼。则天下皆归于仁云尔。归仁是克己之效。而一日自属克复地头。又按天下归仁有二义。一则以仁归之也。一则归于吾仁也。集注云与其仁。而小注用伊川说。作称其仁。恐不若归其仁之为稳。大全答连嵩卿,杨子顺书。皆以称仁言。答石子重书。以后本说为正。而大全中凡三变其说。窃恐答石书。似为定论。然但与集注不合可疑。
司马牛不忧不惧章。
按向魋作乱。而牛以至亲。可得无忧惧乎。窃谓当忧而安得不忧。当惧而安得不惧。但兄之恶非己力可止。祸患之来。非忧惧可免。内自省而无愧于心。则亦何可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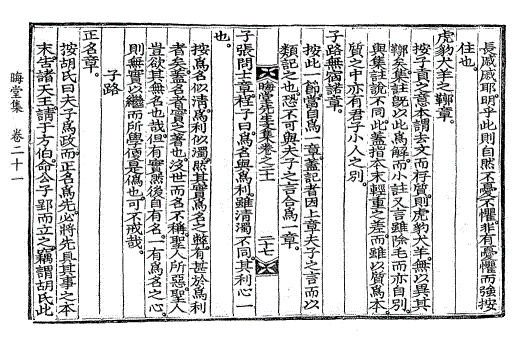 长戚戚耶。明乎此则自然不忧不惧。非有忧惧而强按住也。
长戚戚耶。明乎此则自然不忧不惧。非有忧惧而强按住也。虎豹犬羊之鞟章。
按子贡之意本谓去文而存质。则虎豹犬羊。无以异其鞟矣。集注既以此为解。而小注又言虽除毛而亦自别。与集注说不同。此盖指本末轻重之差。而虽以质为本。质之中亦有君子小人之别。
子路无宿诺章。
按此一节。当自为一章。盖记者因上章夫子之言而以类记之也。恐不可与夫子之言合为一章。
子张问士章。程子曰。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其利心一也。
按为名似清。为利似浊。然其实为名之弊。有甚于为利者矣。盖名者实之著也。没世而名不称。圣人所恶。圣人岂欲其无名也哉。但有实然后自有名。一有为名之心。则无实以继而所学便是伪也。可不戒哉。
子路
正名章。
按胡氏曰夫子为政。而正名为先。必将先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窃谓胡氏此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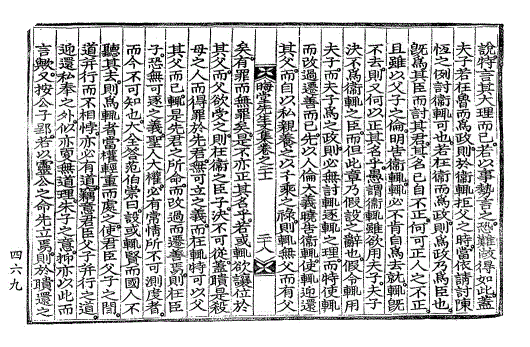 说。特言其大理而已。若以事势言之。恐难做得如此。盖夫子若在鲁而为政。则于卫辄拒父之时。当依请讨陈恒之例讨卫辄可也。若在卫而为政。则为政乃为臣也。既为其臣而讨其君。其名已自不正。何可正人之不正。且虽以父子之伦。明告卫辄。辄必不肯自为去就。辄既不去。则又何以正其名乎。愚谓卫辄虽欲用夫子。夫子决不为卫辄之臣。而但此章乃假设之辞也。假令辄用夫子。而夫子为之政。则必无讨辄逐辄之理。而特使辄而改过迁善而已。先以人伦大义晓告卫辄。使辄迎还其父。而自以私亲养之以千乘之禄。则辄无父而有父矣。有罪而无罪矣。是不亦正其名乎。若或辄欲让位于其父。而父欲受之。则在卫之臣子。决不可从。盖聩是杀母之人而得罪于先君。无可立之义。而在辄特可以父其父而已。辄是先君之所命。而改过而迁善焉。则在臣子。恐无可逐之义。圣人大权。必有常情所不可测度者。而今不可知也。大全答范伯崇曰。设或辄贤而国人不听其去。则为辄者当权轻重而处之。使君臣父子之间。道并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窃意君臣父子并行之道。迎还私奉之外。似亦更无道理。朱子之意。抑亦以此而言欤。又按公子郢。若以灵公之命先立焉。则于聩还之
说。特言其大理而已。若以事势言之。恐难做得如此。盖夫子若在鲁而为政。则于卫辄拒父之时。当依请讨陈恒之例讨卫辄可也。若在卫而为政。则为政乃为臣也。既为其臣而讨其君。其名已自不正。何可正人之不正。且虽以父子之伦。明告卫辄。辄必不肯自为去就。辄既不去。则又何以正其名乎。愚谓卫辄虽欲用夫子。夫子决不为卫辄之臣。而但此章乃假设之辞也。假令辄用夫子。而夫子为之政。则必无讨辄逐辄之理。而特使辄而改过迁善而已。先以人伦大义晓告卫辄。使辄迎还其父。而自以私亲养之以千乘之禄。则辄无父而有父矣。有罪而无罪矣。是不亦正其名乎。若或辄欲让位于其父。而父欲受之。则在卫之臣子。决不可从。盖聩是杀母之人而得罪于先君。无可立之义。而在辄特可以父其父而已。辄是先君之所命。而改过而迁善焉。则在臣子。恐无可逐之义。圣人大权。必有常情所不可测度者。而今不可知也。大全答范伯崇曰。设或辄贤而国人不听其去。则为辄者当权轻重而处之。使君臣父子之间。道并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窃意君臣父子并行之道。迎还私奉之外。似亦更无道理。朱子之意。抑亦以此而言欤。又按公子郢。若以灵公之命先立焉。则于聩还之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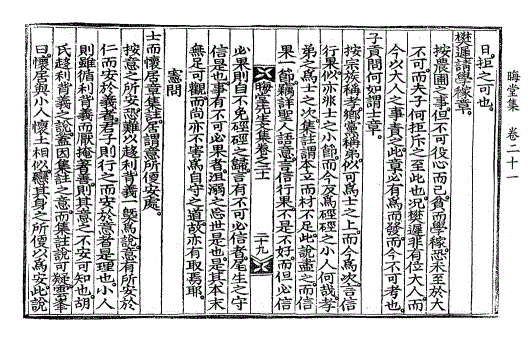 日。拒之可也。
日。拒之可也。樊迟请学稼章。
按农圃之事。但不可役心而已。贫而学稼。恐未至于大不可。而夫子何拒斥之至此也。况樊迟非有位大人。而今以大人之事责之。此章必有为而发。而今不可考也。
子贡问何如谓士章。
按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似可为士之上。而今为次。言信行果。似亦非士之小节。而今反为硁硁之小人何哉。孝弟之为士之次。集注谓本立而材不足。此说尽之。而信果一节。窃详圣人语意。言信行果。不是不好。而但必信必果则自不免硁硁之归。言有不可必信者。尾生之守信是也。事有不可必果者。沮溺之忘世是也。是其本末无足可观。而尚亦不害为自守之道。故亦有取焉耶。
宪问
士而怀居章集注。居谓意所便安处。
按意之所安。恐难以趍利背义一槩为说。意有所安于仁而安于义者。君子则行之而安于意者是理也。小人则虽循利背义而厌掩著善。则其意之不安可知也。胡氏趍利背义之说。盖因集注之意。而集注说可疑。云峰曰。怀居与小人怀土相似。恋其身之所便以为安。此说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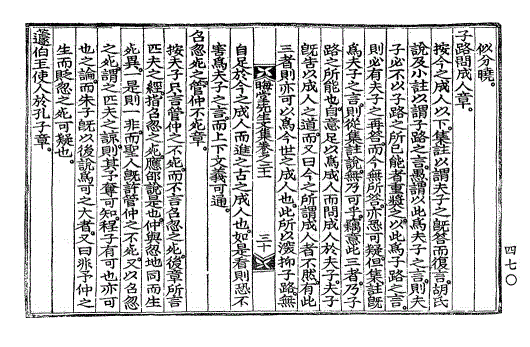 似分晓。
似分晓。子路问成人章。
按今之成人以下。集注以谓夫子之既答而复言。胡氏说及小注以谓子路之言。愚谓以此为夫子之言。则夫子必不以子路之所已能者重奖之。以此为子路之言。则必有夫子之再答。而今无所答。亦恐可疑。但集注既为夫子之言。则从集注说。无乃可乎。窃意此三者。乃子路之所能也。自意足以为成人而问成人于夫子。夫子既告以成人之道。而又曰今之所谓成人者不然。有此三者则亦可以为今世之成人也。此所以深抑子路。无自足于今之成人而进之古之成人也。如是看则恐不害为夫子之言。而上下文义可通。
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章。
按夫子只言管仲之不死。而不言召忽之死。后章所言匹夫之经。指召忽之死。应邵说是也。仲与忽地同而生死异。一是则一非。而圣人既许管仲之不死。又以召忽之死。谓之匹夫之谅。则其予夺可知。程子有可也亦可也之论。而朱子既以后说为可之大者。又曰非予仲之生而贬忽之死可疑也。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1H 页
 按圣人凡于称人善。必俟其出。斥人亦俟其出。盖面称人近阿。面斥人亦近迫切。圣人气象。推此可知。而所当为法者也。
按圣人凡于称人善。必俟其出。斥人亦俟其出。盖面称人近阿。面斥人亦近迫切。圣人气象。推此可知。而所当为法者也。公伯寮愬子路章。朱子曰。此章所谓命。指气言。
按命是天理之流行。而今谓之气者何也。窃谓指其流行者而言。则为万物之体。而流行不穷者是理也。指其作用者而言。则气有不齐。理在其中。而废兴运动者是气也。中庸所谓天命之命。是指不杂气底本体而言。此章所谓命。是指气数之运用者言。所指各不同。
作者七人章。
按此章似是七卷逸民章之文错简在此。盖此章未知其所指之为谁。而语无端绪。圣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含糊也。移在逸民章柳下惠小连之下。则文理接续。语脉分明。此为错简无疑。
原壤夷俟章。
按朱子曰大故在所当绝。损友亦所当远。原壤母死而歌。其灭礼无道。未必非大故也。而圣人尚有亲之之意而以故人视之。盖非常人之情所可测识也。
卫灵公
无为而治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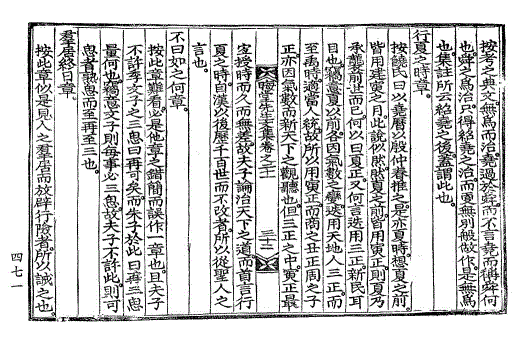 按考之典文。无为而治。尧过于舜。而不言尧而称舜何也。舜之为治。只得绍尧之治。而更无别般做作。是无为也。集注所云绍尧之后。盖谓此也。
按考之典文。无为而治。尧过于舜。而不言尧而称舜何也。舜之为治。只得绍尧之治。而更无别般做作。是无为也。集注所云绍尧之后。盖谓此也。行夏之时章。
按饶氏曰以尧历以殷仲春推之。是亦夏时。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此说似然。然夏之前。皆用寅正。则夏乃承袭前世而已。何以曰夏正。又何言迭用三正。新民耳目也。窃意夏以前。各因气数之变。迭用天地人三正。而至禹时。适当人统。故所以用寅正。而商之丑正周之子正。亦因气数而新天下之观听也。但三正之中。寅正最宜授时而久而无差。故夫子论治天下之道。而首言行夏之时。自汉以后历千百世而不改者。所以从圣人之言也。
不曰如之何章。
按此章难看。必是他章之错简而误作一章也。且夫子不许季文子之三思曰再可矣。而朱子于此曰再三思量何也。窃意文子则每事必三思。故夫子不许此。则可思者熟思而至再至三也。
群居终日章。
按此章似是见人之群居而放辟行险者。所以诫之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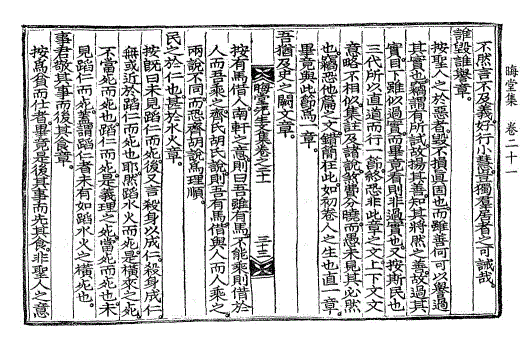 不然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岂独群居者之可诫哉。
不然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岂独群居者之可诫哉。谁毁谁誉章。
按圣人之于恶者。毁不损真固也。而虽善何可以誉过其实也。窃谓有所试。故扬其善。知其将然之善。故过其实。目下虽似过实。而毕竟看则非过实也。又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一节。终恐非此章之文。上下文文意略不相似。集注及诸说。煞费分晓。而愚未见其必然也。窃恐他篇之文。错简在此。如初卷人之生也直一章。毕竟与此节为一章。
吾犹及史之阙文章。
按有马借人。南轩之意。则曰吾虽有马。不能乘则借于人而吾乘之。齐氏胡氏说。则吾有马。借与人而人乘之。两说不同。而恐齐胡说为理顺。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章。
按既曰未见蹈仁而死。后又言杀身以成仁。杀身成仁。无或近于蹈仁而死也耶。然蹈水火而死。是横来之死。不当死而死也。蹈仁而死。是义理之死。当死而死也。未见蹈仁而死。盖谓蹈仁者未有如蹈水火之横死也。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章。
按为贫而仕者。毕竟是后其事而先其食。非圣人之意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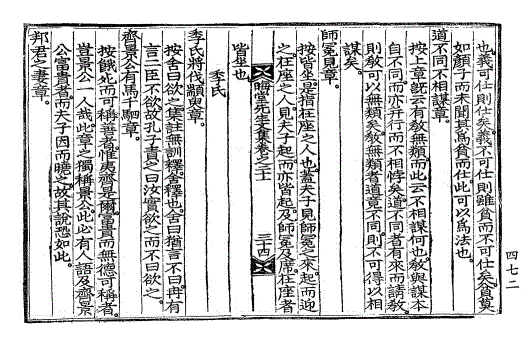 也。义可仕则仕矣。义不可仕则虽贫而不可仕矣。贫莫如颜子而未闻其为贫而仕。此可以为法也。
也。义可仕则仕矣。义不可仕则虽贫而不可仕矣。贫莫如颜子而未闻其为贫而仕。此可以为法也。道不同不相谋章。
按上章既云有教无类。而此云不相谋何也。教与谋本自不同。而亦并行而不相悖矣。道不同者有来而请教。则教可以无类矣。教无类者道竟不同。则不可得以相谋矣。
师冕见章。
按皆坐。是指在座之人也。盖夫子见师冕之来。起而迎之。在座之人。见夫子起。而亦皆起。及师冕及席。在座者皆坐也。
季氏
季氏将伐颛臾章。
按舍曰欲之。集注无训释。舍释也。舍曰犹言不曰。冉有言二臣不欲。故孔子责之曰汝实欲之而不曰欲之。
齐景公有马千驷章。
按饿死而可称善者。惟夷齐是尔。富贵而无德可称者。岂景公一人哉。此章之独称景公。此必有人语及齐景公富贵者。而夫子因而晓之。故其说恐如此。
邦君之妻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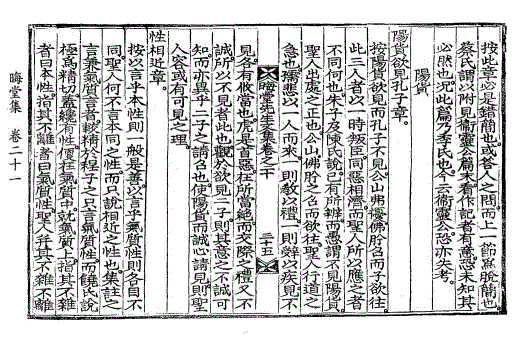 按此章必是错简也。或答人之问。而上一节为脱简也。蔡氏谓以附见卫灵公篇末。看作记者有意。恐未知其必然也。况此篇乃季氏也。今云卫灵公。恐亦失考。
按此章必是错简也。或答人之问。而上一节为脱简也。蔡氏谓以附见卫灵公篇末。看作记者有意。恐未知其必然也。况此篇乃季氏也。今云卫灵公。恐亦失考。阳货
阳货欲见孔子章。
按阳货欲见而孔子不见。公山弗扰,佛肸召而子欲往。此三人者以一时叛臣。同恶相济。而圣人所以应之者不同何也。朱子及陈氏说。已有所辨。而愚谓不见阳货。圣人出处之正也。公山,佛肸之召而欲往。圣人行道之急也。孺悲以一人而来。一则教以礼。一则辞以疾。见不见。各有攸当也。虎是首恶。在所当绝。而交际之礼又不诚。所以不见者此也。观于欲见二子。则其意之不诚可知。而亦异乎二子之请召也。使阳货而诚心请见。则圣人容或有可见之理。
性相近章。
按以言乎本性则一般是善。以言乎气质性则各自不同。圣人何不言本同之性。而只说相近之性也。集注之言兼气质言者。较精于程子之只言气质性。而饶氏说极为精切。盖才有性。便在气质中。就气质上。指其不杂者曰本性。指其不离者曰气质性。圣人并其不杂不离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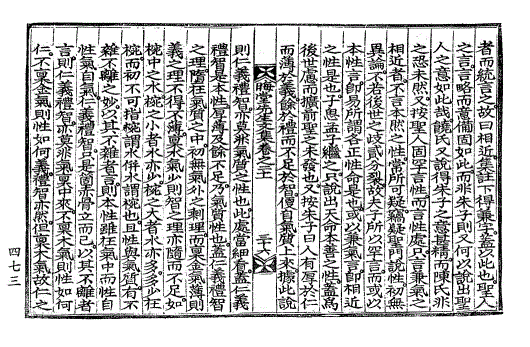 者而统言之。故曰相近。集注下得兼字。盖以此也。圣人之言。言略而意备固如此。而非朱子则又何以说出圣人之意如此哉。饶氏又说得朱子之意甚精。而陈氏非之恐未然。又按圣人固罕言性。而言性处。只言兼气之相近者。不言本然之性。常所可疑。窃疑圣门说性。初无异论。不若后世之歧贰分裂。故夫子所以罕言。而或以本性言。即易所谓各正性命是也。或以兼气言。即相近之性是也。子思孟子继之。只说出天命本善之性。盖为后世虑而扩前圣之未发也。又按朱子曰人有厚于仁而薄于义。馀于礼而不足于智。便自气质上来。据此说则仁义礼智。亦莫非气质之性也。此处当细看。盖仁义礼智是本性。厚薄及馀不足。乃气质性也。盖仁义礼智之理。堕在气质之中。初无气外之剩理。而禀金气薄则义之理不得不薄。禀水气少则智之理亦随而不足。如碗中之水。碗之小者水亦少。碗之大者水亦多。多少在碗。而初不可指碗谓水并水谓碗也。且性与气质。有不杂不离之妙。以其不杂者言。则本性虽在气中而性自性气自气。仁义礼智。只是个赤骨立而已。以其不离者言。则仁义礼智。亦莫非气禀中来。不禀木气则性如何仁。不禀金气则性如何义。礼智亦然。但禀木气故仁之
者而统言之。故曰相近。集注下得兼字。盖以此也。圣人之言。言略而意备固如此。而非朱子则又何以说出圣人之意如此哉。饶氏又说得朱子之意甚精。而陈氏非之恐未然。又按圣人固罕言性。而言性处。只言兼气之相近者。不言本然之性。常所可疑。窃疑圣门说性。初无异论。不若后世之歧贰分裂。故夫子所以罕言。而或以本性言。即易所谓各正性命是也。或以兼气言。即相近之性是也。子思孟子继之。只说出天命本善之性。盖为后世虑而扩前圣之未发也。又按朱子曰人有厚于仁而薄于义。馀于礼而不足于智。便自气质上来。据此说则仁义礼智。亦莫非气质之性也。此处当细看。盖仁义礼智是本性。厚薄及馀不足。乃气质性也。盖仁义礼智之理。堕在气质之中。初无气外之剩理。而禀金气薄则义之理不得不薄。禀水气少则智之理亦随而不足。如碗中之水。碗之小者水亦少。碗之大者水亦多。多少在碗。而初不可指碗谓水并水谓碗也。且性与气质。有不杂不离之妙。以其不杂者言。则本性虽在气中而性自性气自气。仁义礼智。只是个赤骨立而已。以其不离者言。则仁义礼智。亦莫非气禀中来。不禀木气则性如何仁。不禀金气则性如何义。礼智亦然。但禀木气故仁之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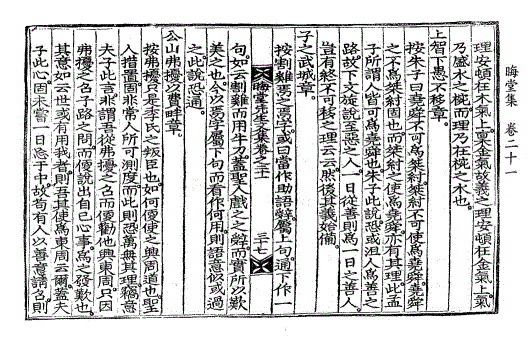 理安顿在木气上。禀金气故义之理安顿在金气上。气乃盛水之碗。而理乃在碗之水也。
理安顿在木气上。禀金气故义之理安顿在金气上。气乃盛水之碗。而理乃在碗之水也。上智下愚不移章。
按朱子曰尧舜不可为桀纣。桀纣不可使为尧舜。尧舜之不为桀纣固也。而桀纣之使为尧舜。亦有其理。此孟子所谓人皆可为尧舜也。朱子此说。恐或沮人为善之路。故下文旋说至恶之人。一日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岂有终不可移之理云云。然后其义始备。
子之武城章。
按割鸡焉之焉字。或曰当作助语辞。属上句。通下作一句。如云割鸡而用牛刀。盖圣人戏之之辞。而实所以叹美之也。今以焉字属下句而看作何用。则语意似或过之。此说恐通。
公山弗扰以费畔章。
按弗扰只是季氏之叛臣也。如何便使之兴周道也。圣人措置。固非常人所可测度。而此则恐万无其理。窃意夫子此言。非谓吾从弗扰之召而便劝他兴东周。只因弗扰之召子路之问。而便说出自己心事。为之发叹也。其意如云世或有用我者。则吾其使为东周云尔。盖夫子此心。固未尝一日忘于中。故苟有人以善意请召。则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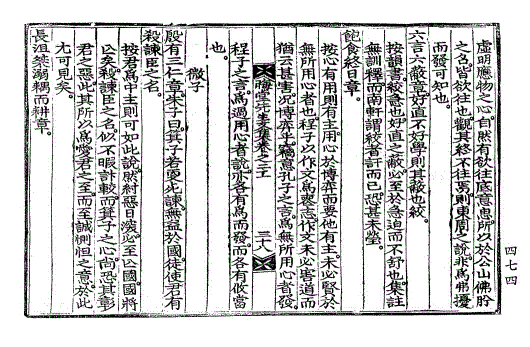 虚明应物之心。自然有欲往底意思。所以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也。观其终不往焉。则东周之说。非为弗扰而发可知也。
虚明应物之心。自然有欲往底意思。所以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也。观其终不往焉。则东周之说。非为弗扰而发可知也。六言六蔽章。好直不好学则其蔽也绞。
按韵书。绞急也。好直之蔽。必至于急迫而不舒也。集注无训释。而南轩谓绞者讦而已。恐甚未莹。
饱食终日章。
按心有用则有主。用心于博弈而要他有主。未必贤于无所用心者也。程子以作文为丧志。作文未必害道而犹云甚害。况博弈乎。窃意孔子之言。为无所用心者发。程子之言。为过用心者说。亦各有为而发。而各有攸当也。
微子
殷有三仁章。朱子曰。箕子若更死谏。无益于国。徒使君有杀谏臣之名。
按君为中主则可如此说。然纣恶日深。必至亡国。国将亡矣。杀谏臣之名。似不暇计较。而箕子之心。尚恐其彰君之恶。此其所以为爱君之至。而至诚恻怛之意。于此尤可见矣。
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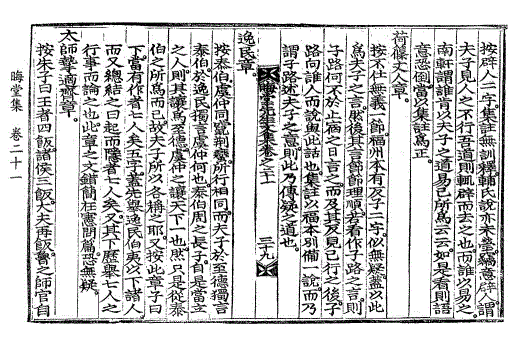 按辟人二字。集注无训释。辅氏说亦未莹。窃意辟人。谓夫子见人之不行吾道则辄辟而去之也。而谁以易之。南轩谓谁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为云云。如是看则语意恐倒。当以集注为正。
按辟人二字。集注无训释。辅氏说亦未莹。窃意辟人。谓夫子见人之不行吾道则辄辟而去之也。而谁以易之。南轩谓谁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为云云。如是看则语意恐倒。当以集注为正。荷筱丈人章。
按不仕无义一节。福州本有反子二字。似无疑。盖以此为夫子之言。然后其言节节理顺。若看作子路之言。则子路何不于止宿之日言之。而及其反见已行之后。子路向谁人而说与此话也。集注以福本别备一说。而乃谓子路述夫子之意。则此乃传疑之道也。
逸民章。
按泰伯,虞仲同窜荆蛮。所行相同。而夫子于至德独言泰伯。于逸民独言虞仲何也。泰伯周之长子。自是当立之人。则其让为至德。虞仲之让天下一也。然只是从泰伯之所为而已。故夫子所以各称之耶。又按此章子曰下。当有作者七人矣五字。盖先举逸民伯夷以下诸人。而又总结之曰起而隐者七人矣。又其下历举七人之行事而论之也。此章之文错简在宪问篇。恐无疑。
太师挚适齐章。
按朱子曰王者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鲁之师官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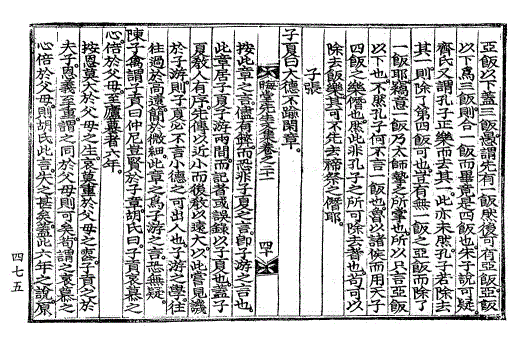 亚饭以下盖三饭。愚谓先有一饭然后可有亚饭。亚饭以下为三饭。则合一饭而毕竟是四饭也。朱子说可疑。齐氏又谓孔子正乐而去其一。此亦未然。孔子若除去其一。则除了第四饭可也。岂有无一饭之亚饭而除了一饭耶。窃意一饭乃太师挚之所掌也。所以只言亚饭以下也。不然孔子何不言一饭也。鲁以诸侯而用天子四饭之乐僭也。然此非孔子之所可除去者也。苟可以除去饭乐。其可不先去禘祭之僭耶。
亚饭以下盖三饭。愚谓先有一饭然后可有亚饭。亚饭以下为三饭。则合一饭而毕竟是四饭也。朱子说可疑。齐氏又谓孔子正乐而去其一。此亦未然。孔子若除去其一。则除了第四饭可也。岂有无一饭之亚饭而除了一饭耶。窃意一饭乃太师挚之所掌也。所以只言亚饭以下也。不然孔子何不言一饭也。鲁以诸侯而用天子四饭之乐僭也。然此非孔子之所可除去者也。苟可以除去饭乐。其可不先去禘祭之僭耶。子张
子夏曰大德不踰闲章。
按此章之言。尽有弊。而恐非子夏之言。即子游之言也。此章居子夏子游两间。而记者或误录以子夏也。盖子夏教人有序。先传以近小而后教以远大。以此尝见讥于子游。则子夏必不言小德之可出人也。子游之学。往往过于高远。简于微细。此章之为子游之言。恐无疑。
陈子禽谓子贡曰仲尼岂贤于子章。胡氏曰。子贡哀慕之心。倍于父母。至庐墓者六年。
按恩莫大于父母之生。哀莫重于父母之丧。子贡之于夫子。恩义至重。谓之同于父母则可矣。苟谓之哀慕之心倍于父母。则胡氏此言。失之甚矣。盖此六年之说。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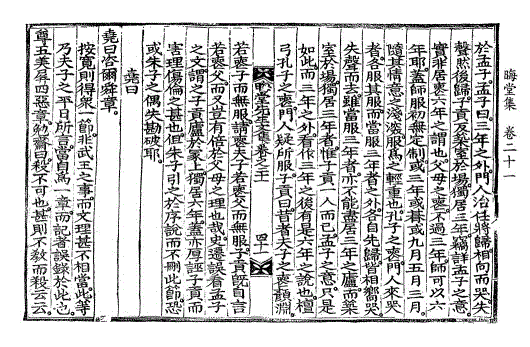 于孟子。孟子曰。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窃详孟子之意。实非居丧六年之谓也。父母之丧。不过三年。师可以六年耶。盖师服初无定制。或三年或期或九月五月三月。随其情意之浅深。服为之轻重也。孔子之丧。门人来哭者。各服其服。而当服三年者之外。各自先归。皆相向哭。失声而去。虽当服三年者。亦不能尽居三年之庐。而筑室于场。独居三年者。惟子贡一人而已。孟子之意。只是如此。而三年之外。看作三年之后有是六年之说也。檀弓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子贡既自言若丧父。而又岂有倍于父母之理也哉。史迁误看孟子之文。谓之子贡庐于冢上。独居六年。盖亦厚诬子贡而害理伤伦之甚也。但朱子引之于序说而不删此节。恐或朱子之偶失勘破耶。
于孟子。孟子曰。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窃详孟子之意。实非居丧六年之谓也。父母之丧。不过三年。师可以六年耶。盖师服初无定制。或三年或期或九月五月三月。随其情意之浅深。服为之轻重也。孔子之丧。门人来哭者。各服其服。而当服三年者之外。各自先归。皆相向哭。失声而去。虽当服三年者。亦不能尽居三年之庐。而筑室于场。独居三年者。惟子贡一人而已。孟子之意。只是如此。而三年之外。看作三年之后有是六年之说也。檀弓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子贡既自言若丧父。而又岂有倍于父母之理也哉。史迁误看孟子之文。谓之子贡庐于冢上。独居六年。盖亦厚诬子贡而害理伤伦之甚也。但朱子引之于序说而不删此节。恐或朱子之偶失勘破耶。尧曰
尧曰咨尔舜章。
按宽则得众一节。非武王之事。而文理甚不相当。此等乃夫子之平日所言。当自为一章。而记者误录于此也。
尊五美屏四恶章。勉斋曰。杀不可也。甚则不教而杀云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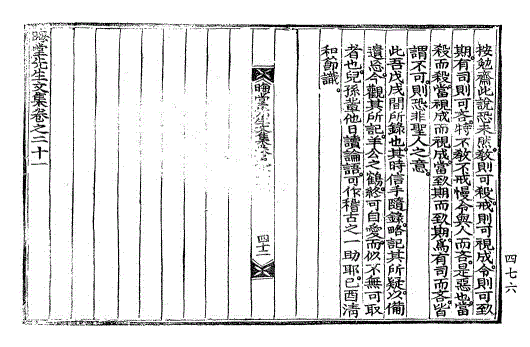 按勉斋此说恐未然。教则可杀。戒则可视成。令则可致期。有司则可吝。特不教不戒慢令与人而吝。是恶也。当杀而杀。当视成而视成。当致期而致期。为有司而吝。皆谓不可。则恐非圣人之意。
按勉斋此说恐未然。教则可杀。戒则可视成。令则可致期。有司则可吝。特不教不戒慢令与人而吝。是恶也。当杀而杀。当视成而视成。当致期而致期。为有司而吝。皆谓不可。则恐非圣人之意。此吾戊戌间所录也。其时信手随录。略记其所疑。以备遗忘。今观其所记。羊公之鹤。终可自爱。而似不无可取者也。儿孙辈他日读论语。可作稽古之一助耶。己酉清和节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