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书
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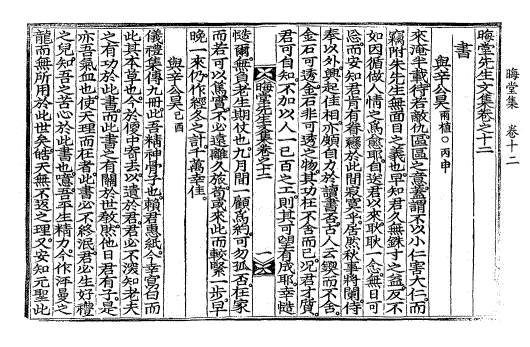 与辛公昊(雨植○丙申)
与辛公昊(雨植○丙申)来淹半载。待若敌仇。区区之意。盖谓不以小仁害大仁。而窃附朱先生无面目之义也。早知君久无铢寸之益。反不如因循做人情之为愈耶。自送君以来。耿耿一念。无日可忘。而安知君肯有眷恋于此间寂寞乎。居然秋事将阑。侍奉以外。兴起佳相。亦颇自力于读书否。古人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透。金石非可透之物。其功在不舍而已。况君才质。君可自知。不加以人一己百之工。则其可望有成耶。幸慥慥尔。无负老生期仗也。九月间一顾为约。可勿孤否。在家而若可以笃实。不必远离久旅。苟或来此而较紧一步。早晚一来。仍作经冬之计。千万幸佳。
与辛公昊(己酉)
仪礼集传九册。此吾精神骨子也。赖君惠纸。今幸写白而此其本草也。今于便中寄去。以遗于君。君必不深知老夫之有功于此书。而此书之有关于世教。然他日君有子。是亦吾气血也。使天理而在者。此书必不终泯。君必生好礼之儿。知吾之苦心于此书也。噫。吾平生精力。今作泙曼之龙而无所用于此世矣。皓天无不返之理。又安知元圣此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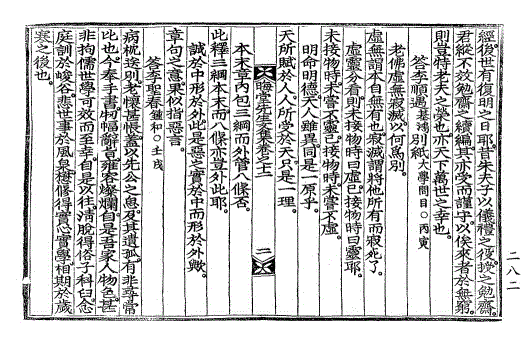 经。后世有复明之日耶。昔朱夫子以仪礼之役。授之勉斋。君纵不效勉斋之续编。其亦受而谨守。以俟来者于无穷。则岂特老夫之荣也。亦天下万世之幸也。
经。后世有复明之日耶。昔朱夫子以仪礼之役。授之勉斋。君纵不效勉斋之续编。其亦受而谨守。以俟来者于无穷。则岂特老夫之荣也。亦天下万世之幸也。答李顺遇(基鸿)别纸(大学问目○丙寅)
老佛虚无寂灭。以何为别。
虚无谓本自无有也。寂灭谓将他所有而寂死了。
虚灵分看。则未接物时曰虚。已接物时曰灵耶。
未接物时。未尝不灵。已接物时。未尝不虚。
明命明德。天人虽异。同是一原乎。
天所赋于人。人所受于天。只是一理。
本末章内包三纲而外管八条否。
此释三纲本末。而八条亦岂外此耶。
诚于中形于外。此是恶之实于中而形于外欤。
章句之意。果似指恶言。
答李圣春(钟和○壬戌)
病枕送别。老怀甚怅。盖以先公之思。及其遗孤。有非寻常比也。今奉手书。牣幅辞旨。雍容灿烂。自是吾家人物色。甚非拘儒世学可效而至幸。自是以往。清脱得俗子科臼。念庭训于峻谷。悲世事于风泉。懋修得实心实学。相期于岁寒之后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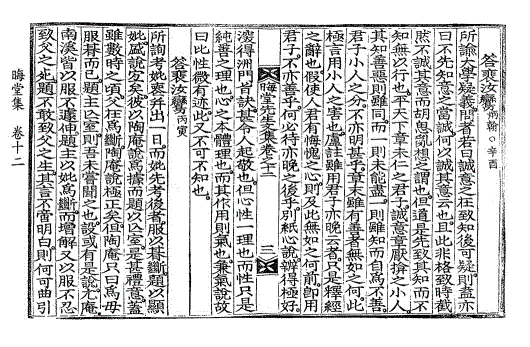 答裴汝鸾(炳翰○辛酉)
答裴汝鸾(炳翰○辛酉)所谕大学疑义。问者若曰诚意之在致知后可疑。则盍亦曰不先知意之当诚。何以诚其意云也。且此非格致时截然不诚其意而胡思乱想之谓也。但道是先致其知而不知无以行也。平天下章未仁之君子。诚意章厌掩之小人。其知善恶则虽同。而一则未能尽。一则虽知而自为不善。君子小人之分。不亦明甚乎。章末虽有善者无如之何。此极言用小人之害也。卢注虽用君子亦晚云者。只是释经之辞也。假使人君有悔愧之心。则及此无如之何前。即用君子。不亦善乎。何必待亦晚之后乎。别纸心说。辨得极好。深得洲门旨诀。甚令人起敬也。但心性一理也。而性只是纯善之理也。心之本体理也。而其作用则气也。兼气说故曰比性微有迹。此又不可不知也。
答裴汝鸾(丙寅)
所询考妣丧并出一日。而妣先考后者。服以期断。题以显妣。盛说宜矣。彼以陶庵说为据而题以亡室。是甚礼意。盖虽数时之顷。父在为断。陶庵说极正矣。但陶庵只曰为母服期而已。题主亡室。则吾未尝闻之也。设或有是说。尤庵,南溪皆以服不遽伸。题主以妣为断。而增解又以服不忍致父之死。题不敢致父之生。其言不啻明白。则何可曲引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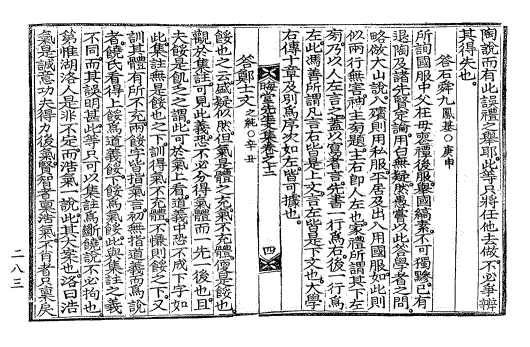 陶说而有此误礼之举耶。此等只将任他去做。不必争辨其得失也。
陶说而有此误礼之举耶。此等只将任他去做。不必争辨其得失也。答石舜九(凤基○庚申)
所询国服中父在母丧禫后服。举国缟素。不可独黪。已有退陶及诸先贤定论。用白无疑。然愚尝以此答学者之问。略仿大山说。入殡则用私服。平居及出入用国服。如此则似两行无害。神主旁题。主右即人左也。家礼所谓其下左旁。乃以人左言之。盖以写者言。先书一行为右。后一行为左。此冯善所谓凡言右皆是上文。言左皆是下文也。大学右传十章及别为序次如左。皆可据也。
答郑士文(之纯○辛丑)
馁也之云。盛疑似然。但气是体之充。气不充体。便是馁也。观于集注。可见此义。恐不必分得气体而一先一后也。且夫馁是饥乏之谓。此可于气上看。道义中恐不成下字如此。集注无是馁也之下。训得气不充体。不慊则馁之下。又训其体有所不充。两馁字皆指气言。初无指道义而为说者。饶氏看得上馁为道义馁。下馁为气馁。此与集注之义不同。而其误明甚。此等只可以集注为断。饶说不必拘也。第惟湖洛人是非不定。而浩气一说。此其大案也。洛曰浩气是诚意功夫得力后气。贤智者禀浩气。不肖者只禀戾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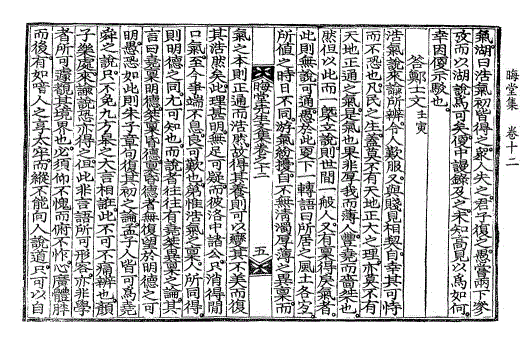 气。湖曰浩气初皆得之。众人失之。君子复之。愚尝两下参考而以湖说为可矣。便中谩录及之。未知高见以为如何。幸因便示驳也。
气。湖曰浩气初皆得之。众人失之。君子复之。愚尝两下参考而以湖说为可矣。便中谩录及之。未知高见以为如何。幸因便示驳也。答郑士文(壬寅)
浩气说来谕所辨。令人叹服。又与贱见相契。自幸其可恃而不恐也。凡民之生。盖莫不有天地正大之理。亦莫不有天地正通之气。是气也果非厚我而薄人。丰尧而啬桀也。然但以此而一槩立说。则世间一般人。又有禀得戾气者。此则无说可通。愚于此更下一转语曰所居之风土各宜。所值之时日不同。游气纷扰。自不无清浊厚薄之异禀。而气之本则正通而浩然。故得其养则可以变其不美而复其浩然矣。此理甚明。无足可疑。而彼洛中诸公。只消得閒口气。至今争端不息。良可叹也。第惟浩气之禀。人所同得。则明德之同。尤可知也。而说者往往有尧桀异禀之论。其言曰尧禀明德。桀禀昏德。禀昏德者无复望于明德之可明。愚恐如此则朱子章句复其初之论。孟子人皆可为尧舜之说。只不免九方皋之大言相诳。此不可不痛辨也。颜子乐处。来谕说恐亦得之。但此非言语所可形容。亦非学者所可遽睹其境界也。必须仰不愧而俯不怍。心广体胖而后。有如喑人之享太牢。而纵不能向人说道。只可以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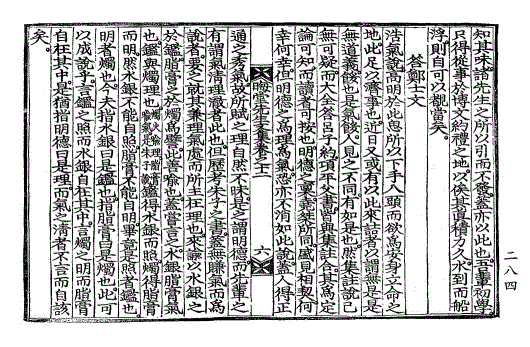 知其味。诸先生之所以引而不发。盖亦以此也。吾辈初学。只得从事于博文约礼之地。以俟其真积力久。水到而船浮。则自可以睹当矣。
知其味。诸先生之所以引而不发。盖亦以此也。吾辈初学。只得从事于博文约礼之地。以俟其真积力久。水到而船浮。则自可以睹当矣。答郑士文
浩气说。高明于此思所以下手入头而欲为安身立命之地。此足以济事也。近日又或有以此来诘者以谓无是是无道义。馁也是气馁。人见之不同。有如是也。然集注说已无可疑。而大全答吕子约,项平父书。皆与集注合。其为定论可知。而读者可按也。明德之禀。尧桀所同。盛见相契。何幸何幸。但明德之为理为气。恐亦不消如此说。盖人得正通之秀气。故所赋之理自然不昧。是之谓明德。而先辈之有谓气清理澈者此也。但历考朱子之书。盖无赚气而为说者。要之就其兼理气处而所主在理也。来谕以水银之于鉴。脂膏之于烛为譬。此善喻也。盖尝言之。水银脂膏气也。鉴与烛理也。(烛火喻理。脂膏喻气。是朱子说。)鉴得水银而照。烛得脂膏而明。然水银不能自照。脂膏不能自明。毕竟是照者鉴也。明者烛也。今夫指水银曰是鉴也。指脂膏曰是烛也。此可以成说乎。言鉴之照而水银自在其中。言烛之明而脂膏自在其中。是犹指明德曰是理。而气之清者不言而自该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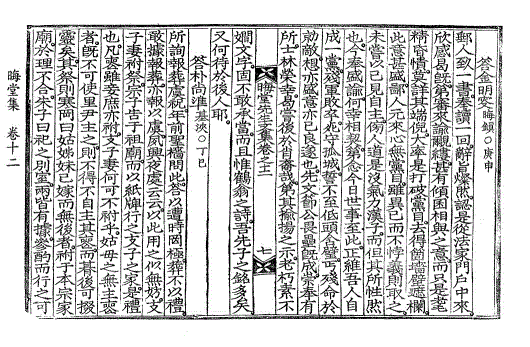 答金明叟(晦镇○庚申)
答金明叟(晦镇○庚申)邮人致一书。奉读一回。辞旨灿然。认是从法家门户中来。欣感曷既。第审来谕覼缕。甚有倾囷相与之意。而只是耄精昏愦。莫详其端倪。大率是打破党目。去得个墙壁遮栏。此意甚盛。鄙人元来心无党目。虽异己而不悖义则取之。未尝以己见自主。傍人道是没气力汉子。而但其所性然也。今奉盛谕。何幸相契。第念今日世事至此。正维吾人自成一党。残军败卒。死守孤城。誓不至低头含璧。丐残命于勍敌。想亦盛意亦已良遂也。先文节公畏垒既成。崇奉有所。士林荣幸。曷尝后于肖裔哉。第其揄扬之示。老朽素不娴文字。固不敢承当。而且惟鹤翁之诗。吾先子之铭多矣。又何待于后人耶。
答朴尚准(基浃○丁巳)
所询报葬虞祝。年前圣樯问此。答以遭时罔极。葬不以礼。敢据报葬。亦报以虞。夙兴夜处云云。以此用之似无妨。支子妻祔祭。宗子告于祖庙。而以纸牌行之支子之家。是礼也。凡丧虽妾庶亦祔。支子妻何可不祔乎。姑母之无主丧者。既不可使里尹主之。则不得不自主其丧。而期后可掇灵矣。其祭则寒冈曰姑姊妹已嫁而无后者。祔于本宗家庙。于理不合。朱子曰祀之别室。两皆有据。参酌而行之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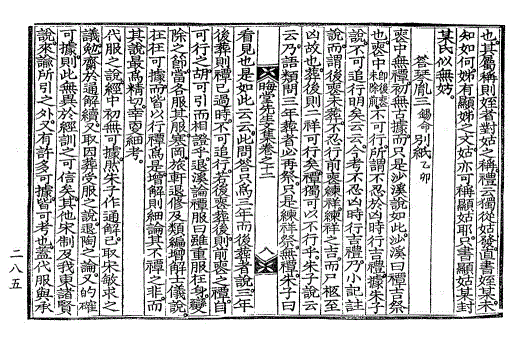 也。其属称则侄者对姑之称。礼云独从姑发。直书侄某。未知如何。姊有显姊之文。姑亦可称显姑耶。只书显姑某封某氏似无妨。
也。其属称则侄者对姑之称。礼云独从姑发。直书侄某。未知如何。姊有显姊之文。姑亦可称显姑耶。只书显姑某封某氏似无妨。答琴胤三(锡命)别纸(乙卯)
丧中无禫。初无古据。而只是沙溪说如此。沙溪曰禫吉祭也。丧中(即后丧未除前。)不可行。所谓不忍于凶时行吉礼。据朱子说。不可追行明矣云云。今考不忍凶时行吉礼。乃小记注说。而谓后丧未葬。不忍行前丧练祥。练祥之吉。而尸柩至凶故也。葬后则二祥可行矣。禫独可以不行乎。朱子说云云。乃语类问三年葬者必再祭。只是练祥祭。无禫。朱子曰看见也是如此云云。此问答只为三年而后葬者说。三年后葬则禫已过时。不可追行。若后丧葬后。则前丧之禫。自可行之。胡可引而相證乎。退溪论禫服曰虽重服在身。变除之节。当各服其服。寒冈,旅轩退修及类编增解士仪说。在在可据。而皆以行禫为是。增解则细论其不禫之非。而其说最为精切。幸更细考。
代服之说。经中初无可据。然朱子作通解。已取宋敏求之议。勉斋于通解续。又取因葬受服之说。退陶之论。又的确可据。则此无异于经训之可信矣。其他宋制及我东诸贤说。来谕所引之外。又有许多可据。皆可考也。盖代服与承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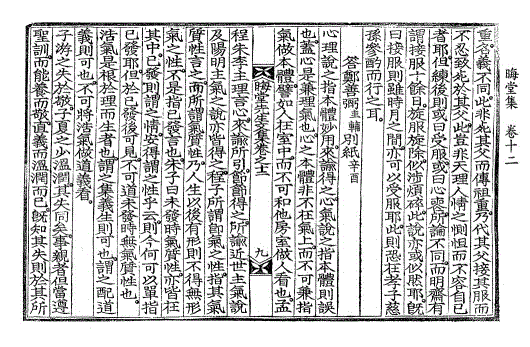 重。名义不同。此非死其父而传祖重。乃代其父接其服而不忍致死于其父。此岂非天理人情之恻怛而不容自已者耶。但练后则或曰受服。或曰心丧。所论不同。而明斋有谓接服十馀日。旋服旋除。似涉烦碎。此说亦或似然耶。既曰接服则虽时月之间。亦可以受服耶。此则恐在孝子慈孙参酌而行之耳。
重。名义不同。此非死其父而传祖重。乃代其父接其服而不忍致死于其父。此岂非天理人情之恻怛而不容自已者耶。但练后则或曰受服。或曰心丧。所论不同。而明斋有谓接服十馀日。旋服旋除。似涉烦碎。此说亦或似然耶。既曰接服则虽时月之间。亦可以受服耶。此则恐在孝子慈孙参酌而行之耳。答郑善弼(圭辅)别纸(辛酉)
心理说之指本体妙用。来谕得之。心气说之指本体则误也。盖心是兼理气也。心之本体非不在气上。而不可兼指气做本体。譬如人在室中。而不可和他房室做人看也。孟程朱李主理言心。来谕所引。节节得之。所谕近世主气说及阳明主气之说亦皆得之。程子所谓即气之性。指其气质性言之。而所谓气质性。乃人生以后有形则不得无形气之性。不是指已发言也。朱子曰未发时气质性。亦皆在其中。已发则谓之情。安得谓之性乎云。则今何可以单指已发耶。但于已发后可见。不可道未发时无气质性也。
浩气是根于理而生者也。谓之集义生则可也。谓之配道义则可也。不可将浩气做道义看。
子游之失于敬。子夏之少温润。其失同矣。事亲者但当遵圣训。而能养而敬。直义而温润而已。既知其失则于其所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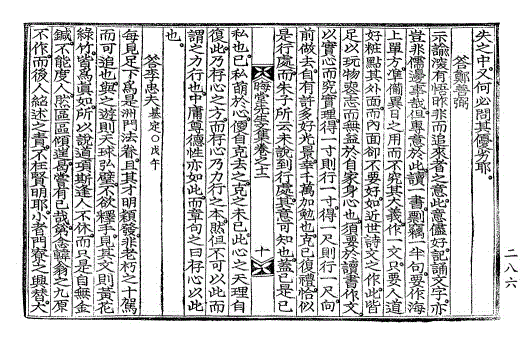 失之中。又何必问其优劣耶。
失之中。又何必问其优劣耶。答郑善弼
示谕深有悟昨非而追来者之意。此意尽好。记诵文字。亦岂非儒边事哉。但专意于此。读一书。剽窃一半句。要作海上单方。准备异日之用而不究其大义。作一文。只要人道好妆点其外面。而内面却不要好。如近世诗文之作。此皆足以玩物丧志而无益于自家身心也。须要于读书作文。以实心而究实理。得一寸则行一寸。得一尺则行一尺。向前做去。自有许多好光景。幸千万加勉也。克己复礼。恰似是行处。而朱子所云未说到行处。其意可知也。盖己是己私也。己私萌于心。便自克去之。克之未已。此心之天理自复。此乃存心之方。而存心乃力行之本。然但不可以此而谓之力行也。中庸尊德性亦如此。而章句之曰存心以此也。
答李忠夫(基定○戊午)
每见足下为是洲门法眷。且其才明颖发。非老朽之十驾而可追也。与之游则天球弘璧。不欲释手。见其文则黄花绿竹。皆为真如。所以说道项斯逢人不休。而只是自无金针。不能度人。然区区倾𨓏。曷尝有已哉。第念韩翁之九原不作。而后人绍述之责。不在贤明耶。小者门寮之兴替。大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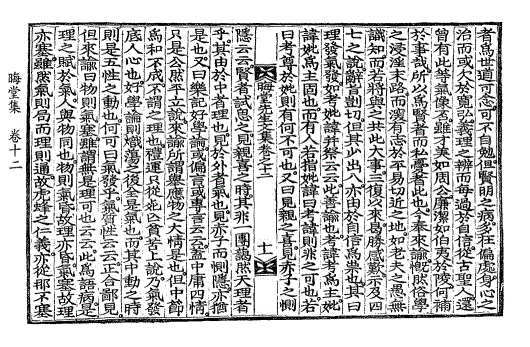 者为世道可念。可不自勉。但贤明之病。多在偏处。身心之治而或欠于宽弘。义理之辨而每过于自信。从古圣人。还曾有此等气像否。虽才美如周公。廉洁如伯夷于陵。何补于事哉。所以为贤者而私忧者此也。今奉来谕。慨然俗学之浸淫末路。而深有志于平易切近之地。如老夫之愚无识知。而若将与之共此大事。三复以来。曷胜感叹。示及四七之说。辞旨剀切。但其少出入。亦由于自信为祟也。其曰理发气发。如考妣讳并祭云云。此善谕也。考讳考为主。妣讳妣为主固也。而有人若指妣讳曰考讳则非之可也。若曰考尊于妣则有何不可也。又曰见亲之喜。见赤子之恻隐云云。贤者试思之。见亲喜之时。其非一团蔼然天理者乎。其由于中者理也。见于外者气也。见赤子而恻隐。亦犹是也。又曰乐记好学论。或偏言或专言云云。盖中庸四情。只是公然平立说。来谕所谓举应物之大情是也。但中节为和不成。不谓之理也。礼运只从死亡贫苦上说。乃气发底人心也。好学论则炽荡之后全是气也。而其中动之时则是五性之动也。何可曰气发乎。气质性云云。正合鄙见。但来谕曰物则气塞。虽谓无是理可也云云。此为语病。是理之赋于气。人与物同也。物则气昏故理亦昏。气塞故理亦塞。虽然气则局而理则通。故虎蜂之仁义。亦从那不塞
者为世道可念。可不自勉。但贤明之病。多在偏处。身心之治而或欠于宽弘。义理之辨而每过于自信。从古圣人。还曾有此等气像否。虽才美如周公。廉洁如伯夷于陵。何补于事哉。所以为贤者而私忧者此也。今奉来谕。慨然俗学之浸淫末路。而深有志于平易切近之地。如老夫之愚无识知。而若将与之共此大事。三复以来。曷胜感叹。示及四七之说。辞旨剀切。但其少出入。亦由于自信为祟也。其曰理发气发。如考妣讳并祭云云。此善谕也。考讳考为主。妣讳妣为主固也。而有人若指妣讳曰考讳则非之可也。若曰考尊于妣则有何不可也。又曰见亲之喜。见赤子之恻隐云云。贤者试思之。见亲喜之时。其非一团蔼然天理者乎。其由于中者理也。见于外者气也。见赤子而恻隐。亦犹是也。又曰乐记好学论。或偏言或专言云云。盖中庸四情。只是公然平立说。来谕所谓举应物之大情是也。但中节为和不成。不谓之理也。礼运只从死亡贫苦上说。乃气发底人心也。好学论则炽荡之后全是气也。而其中动之时则是五性之动也。何可曰气发乎。气质性云云。正合鄙见。但来谕曰物则气塞。虽谓无是理可也云云。此为语病。是理之赋于气。人与物同也。物则气昏故理亦昏。气塞故理亦塞。虽然气则局而理则通。故虎蜂之仁义。亦从那不塞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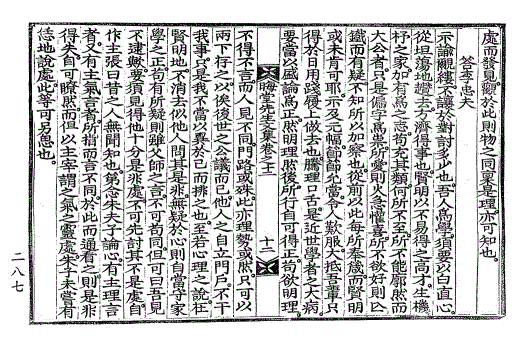 处而发见。观于此则物之同禀是理。亦可知也。
处而发见。观于此则物之同禀是理。亦可知也。答李忠夫
示谕覼缕。不让于对讨多少也。吾人为学。须要以白直心。从坦荡地趱去。方济得事也。贤明以不易得之高才。生机杼之家。加有为之志。苟充其类。何所不至。所不能廓然而大公者。只是偏字为祟。所爱则火急欢喜。所不欲好则亡铁而有疑。不知所以加察也。从前以此每所奉箴。而贤明或未肯可耶。示及元幅。节节允当。令人叹服。大抵吾辈只得于日用践履上做去也。腾理口舌。是近世学者之大病。要当以盛论为正。然明理然后。所行自可得正。苟欲明理。不得不言。而人见不同。门路或殊。此亦理势或然。只可以两下存之。以俟后世之公议而已。他人之自立门户。不干我事。只是我不当以异于己而排之也。至若心理之说。在贤明地。不消去似他人问其是非。无疑于心则自当守家学之正。苟有所疑则虽父师之言。不可苟同。但可曰吾见不逮欤。要须见得他十分是非处。不可先讨其不是处。自作主张曰昔之人无闻知也。第念朱夫子论心。有主理言者。又有主气言者。所指而言不同。于此而通看之。则是非得失。自可瞭然。而但以主宰谓之气之灵处。朱子未尝有恁地说处。此等可另思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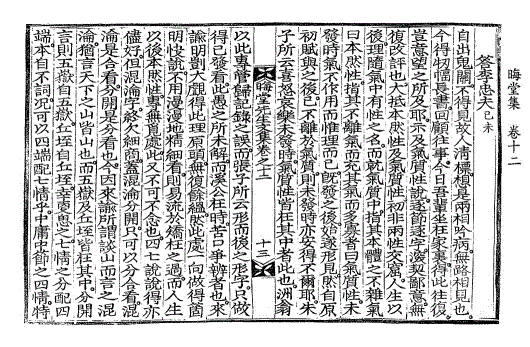 答李忠夫(己未)
答李忠夫(己未)自出鬼关。不得见故人清标。想是两相吟病。无路相见也。今得牣幅长书。回顾往事。今日吾辈坐在家里。得此往复。岂意望之所及耶。示及气质性说。逐节逐字。深契鄙意。无复改评也。大抵本然性及气质性。初非两性交窟。人生以后。理随气中有性之名。而就气质中。指其本体之不杂气曰本然性。指其不离气而充其气而多寡者曰气质性。未发时气不作用而惟理而已。既发之后。始遂形见。然自原初赋与之后。已不离于气质。则未发时亦安得不尔耶。朱子所云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质性皆在其中者此也。洲翁以此专管归记录之误。而张子所云形而后之形字。只做得已发看。此愚之所未解。而溪公在时。苦口争辨者也。来谕明剀大觑得此理原头。无复馀缊。然此处一向做得个明快说。不用漫漫地精细看。则易流于矫枉之过。而人生以后本然性。专无觅处。此又不可不念也。四七说说得亦尽好。但混沦字。终欠细商。盖混沦分开。只可以分合看。混沦是合看。分开是分看也。今因来谕所谓谈山而言之混沦。犹言天下之山皆山也。而五岳及丘垤皆在其中。分开言则五岳自五岳。丘垤自丘垤。幸更思之。七情之分配四端。本自不词。况可以四端配七情乎。中庸中节之四情。特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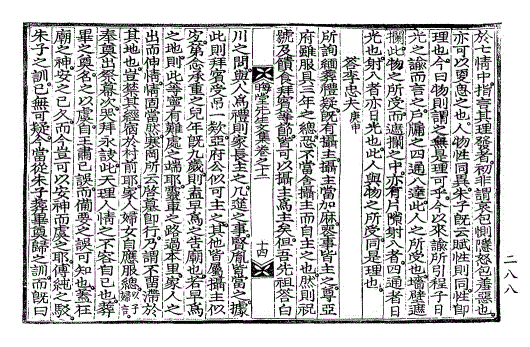 于七情中。指言其理发者。初非谓哀包恻隐怒包羞恶也。亦可以更思之也。人物性同异。朱子既云赋性则同。性即理也。今曰物则谓之无是理可乎。今以来谕所引程子日光之谕而言之。户牖之四通八达。此人之所受也。墙壁遮拦。此物之所受。而遮拦之中。亦有片隙射入者。四通者日光也。射入者亦日光也。此人与物之所受。同是理也。
于七情中。指言其理发者。初非谓哀包恻隐怒包羞恶也。亦可以更思之也。人物性同异。朱子既云赋性则同。性即理也。今曰物则谓之无是理可乎。今以来谕所引程子日光之谕而言之。户牖之四通八达。此人之所受也。墙壁遮拦。此物之所受。而遮拦之中。亦有片隙射入者。四通者日光也。射入者亦日光也。此人与物之所受。同是理也。答李忠夫(庚申)
所询缅葬礼疑。既有摄主。摄主当加麻。丧事皆主之。尊亚府虽服具三年之缌。恐不当舍摄主而自主之也。然则祝号及馈食拜宾等节。皆可以摄主为主矣。但吾先祖答白川之问。与人为礼则家长主之。几筵之事。贤胤皆当之。据此则拜宾受吊一款。亚府公似可主之。其他皆属摄主似宜。第念承重之儿年既九岁。则盍早为之告庙也。若早为之地。则此等宁有难处之端耶。灵车之路过本里。家人之出而伸情。情固当然。寒冈所云启墓即行。乃谓不留滞于其地也。岂禁其经宿于村前耶。家人妇女自应服缌。(以子妇言。)奉奠出祭幕次。哭拜永诀。此天理人情之不容自已也。葬毕之奠。名之以虞。自王肃已误。而备要之误可知也。盖在庙之神。安之已久。而今岂可以安神而虞之耶。傅纯之驳。朱子之训。已无可疑。今当从朱子葬毕奠归之训。而既曰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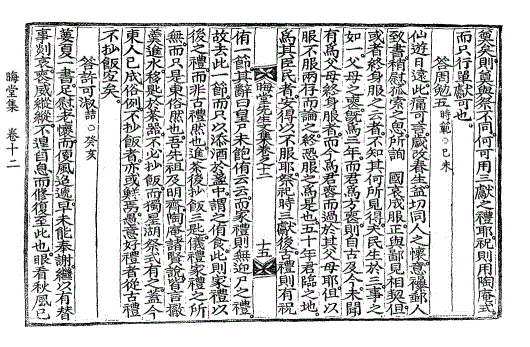 奠矣。则奠与祭不同。何可用三献之礼耶。祝则用陶庵式。而只行单献可也。
奠矣。则奠与祭不同。何可用三献之礼耶。祝则用陶庵式。而只行单献可也。答周勉五(时范○己未)
仙游日远。此痛可言。岁改春生。益切同人之怀。意襮邮人致书。稍慰孤索之思。所询 国哀成服。正与鄙见相契。但或者终身服之云者。不知其何所见得。夫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母之丧。既为三年。而君为方丧。则自古及今。未闻有为父母终身服者。而今为君丧而过于其父母耶。但以服不服两存而论之。终恐服之为是也。五十年君临之地。为其臣民者。安得以不服耶。祭祀时三献后。古礼则有祝侑一节。其辞曰皇尸未饱侑云云。而家礼则无迎尸之礼。故去此一节。而只以添酒于盏中。谓之侑食。此则家礼以后之礼。而非古礼然也。进茶后抄饭三匙。仪礼家礼之所无。而只是东俗然也。吾先祖及明齐,陶庵诸贤说。皆言撤羹进水。移匙于茶器。不必抄饭。而独星湖祭式有之。盖今东人已成俗例。不抄饭者。亦或鲜焉。愚意好礼者从古礼不抄饭宜矣。
答许可淑(哲○癸亥)
葽夏一书。足慰老怀。而便风迢递。早未能奉谢。继以有替事剡哀。丧威纵纵。不遑自息而修复至此也。眼看秋风已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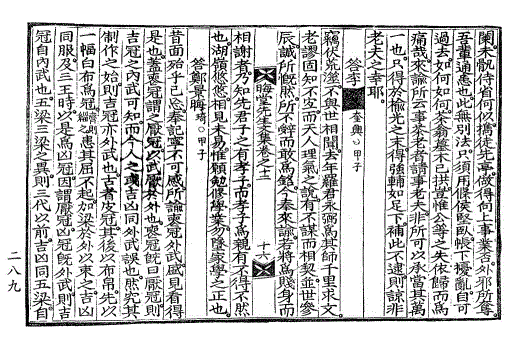 阑。未骫侍省何似。携徒先亭。做得向上事业否。外邪所夺。吾辈通患也。此无别法。只须用条侯坚卧。帐下扰乱。自可过去。如何如何。茶翁墓木已拱。岂惟公等之失依归而为痛哉。来谕所云事茶老者请事老夫。非所可以承当其万一也。只得于榆光之末。得强辅如足下。补此不逮。则谅非老夫之幸耶。
阑。未骫侍省何似。携徒先亭。做得向上事业否。外邪所夺。吾辈通患也。此无别法。只须用条侯坚卧。帐下扰乱。自可过去。如何如何。茶翁墓木已拱。岂惟公等之失依归而为痛哉。来谕所云事茶老者请事老夫。非所可以承当其万一也。只得于榆光之末。得强辅如足下。补此不逮。则谅非老夫之幸耶。答李■■(奎兴○甲子)
窃伏荒澨。不与世相闻。去年罗君永弼为其师千里求文。老谬固知不宜。而天人理气之说。有不谋而相契。并世参辰。诚所慨然。所不辞而敢为铭。今奉来谕。若将为贱身而相谢者。乃知先君子之有孝子。而孝子为亲有不得不然也。湖岭悠悠。相见未易。惟愿勉修学业。勿坠家学之正也。
答郑景晦(琦○甲子)
昔面殆乎已忘。奉记宁不可感。所谕丧冠外武。盛见看得是也。盖丧冠谓之厌冠。以武厌于外也。丧冠既曰厌冠。则吉冠之内武可知。而今人之或吉凶同外武误也。然究其制作之始。则吉冠亦外武也。古者皮冠。其后以布帛。先以一幅白布为冠。(齐则缁之。)患其屈不起。加梁于外以束之。吉凶同服。及三王时。以是为凶冠。因谓厌冠。凶冠既外武。则吉冠自内武也。五梁三梁之异。则三代以前。吉凶同五梁。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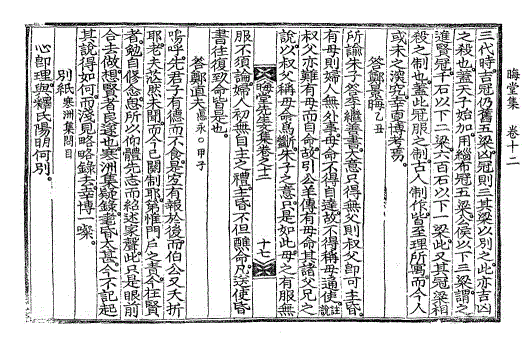 三代时。吉冠仍旧五梁。凶冠则三其梁以别之。此亦吉凶之杀也。盖天子始加。用缁布冠五梁。公侯以下三梁。谓之进贤冠。千石以下二梁。六百石以下一梁。此又其冠梁相杀之制也。盖此冠服之制。古人制作。皆至理所寓。而今人或未之深究。幸更博考焉。
三代时。吉冠仍旧五梁。凶冠则三其梁以别之。此亦吉凶之杀也。盖天子始加。用缁布冠五梁。公侯以下三梁。谓之进贤冠。千石以下二梁。六百石以下一梁。此又其冠梁相杀之制也。盖此冠服之制。古人制作。皆至理所寓。而今人或未之深究。幸更博考焉。答郑景晦(乙丑)
所谕朱子答李继善书。大意只得无父则叔父即可主昏。有母则妇人无外事。母命不得自达。故不得称母通使。(注说)叔父亦难有母而自命。故引公羊传有母命其诸父兄之说。以叔父称母命为断。朱子之意。只是如此。母之有服无服不须论。妇人初无自主之礼。主昏不但醮命。凡送使昏书往复致命皆是也。
答郑直夫(德永○甲子)
呜呼。先君子有德而不食。是宜有报于后。而伯公又夭折耶。老夫茫然未闻。而今已阕制耶。第惟门户之责。今在贤者。勉自修念。思所以仰体先志而绍述家声。此只是眼前合去做。想贤者良遂也。寒洲集疑录。耄昏太甚。今不记起其说得如何。而浅见略略录去。幸博一哂。
别纸(寒洲集问目)
心即理。与释氏阳明何别。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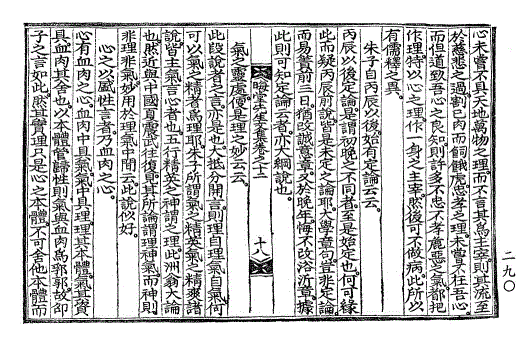 心未尝不具天地万物之理。而不言其为主宰。则其流至于慈悲之过。割己肉而饲饿虎。忠孝之理。未尝不在吾心。而但道致吾心之良知。则许多不忠不孝粗恶之气。都把作理。特以心之理。作一身之主宰。然后可不做病。此所以有儒释之异。
心未尝不具天地万物之理。而不言其为主宰。则其流至于慈悲之过。割己肉而饲饿虎。忠孝之理。未尝不在吾心。而但道致吾心之良知。则许多不忠不孝粗恶之气。都把作理。特以心之理。作一身之主宰。然后可不做病。此所以有儒释之异。朱子自丙辰以后。始有定论云云。
丙辰以后定论。是谓初晚之不同者。至是始定也。何可缘此而疑丙辰前说。皆是未定之论耶。大学章句。岂非定论。而易箦前三日。犹改诚意章。又于晚年。悔不改浴沂章。据此则可知定论云者。亦大纲说也。
气之灵处。便是理之妙云云。
此段说者之言。亦是也。大抵分开言。则理自理气自气。何可以气之精者为理耶。朱子所谓气之精英气之精爽诸说。皆主气言心者也。五行精英之神谓之理。此洲翁大论也。然近与中国夏震武往复。见其所论谓理神气。而神则非理非气。妙用于理气中间云。此说似好。
心之以盛性言者。乃血肉之心。
心有血肉之心。血肉中具气。气中具理。理其本体。气其资具。血肉其舍也。以本体管归性则气与血肉为郛郭。故邵子之言如此。然其实理只是心之本体。不可舍他本体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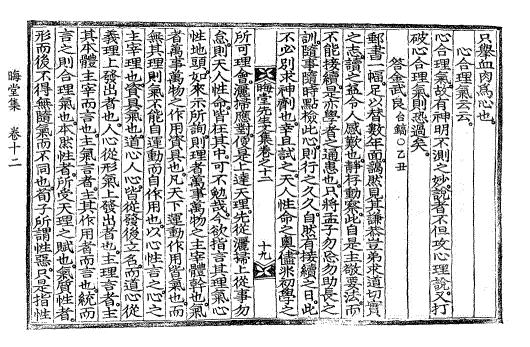 只举血肉为心也。
只举血肉为心也。心合理气云云。
心合理气。故有神明不测之妙。说者不但攻心理说。又打破心合理气则恐过矣。
答金武良(台镐○乙丑)
邮书一幅。足以替数年面。蔼然见其谦恭岂弟求道切实之志。读之益令人感叹也。静存动察。此自是主敬要法。而不能接续。是亦学者之通患也。只将孟子勿忘勿助长之训。随事随时点检此心。则行之久久。自然有接续之日。此不必别求神剂也。幸且试之。天人性命之奥。尽非初学之所可理会。洒扫应对。便是上达天理。先从洒扫上从事勿怠。则天人性命。皆在其中。可不勉哉。今欲指言其理气心性地头。如来示所询。则理者万事万物之主宰体干也。气者万事万物之作用资具也。凡天下运动作用皆气也。而无其理则气不能自运动而自作用也。以心性言之。心之主宰理也。资具气也。道心人心。皆从发后立名。而道心从义理上发出者也。人心从形气上发出者也。主理言者。主其本体主宰而言也。主气言者。主其作用者而言也。统而言之则合理气也。本然性者。所受天理之赋也。气质性者。形而后不得无随气而不同也。荀子所谓性恶。只是指性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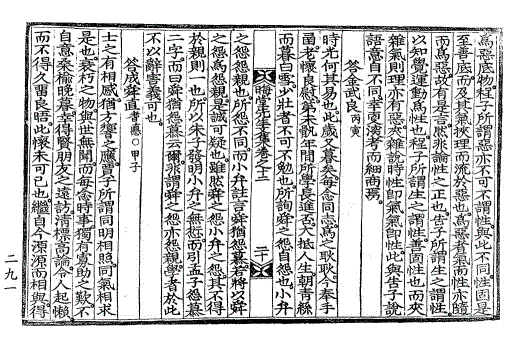 为恶底物。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性。与此不同。性固是至善底。而及其气挟理而流于恶也。为恶者气而性亦随而为恶。故有是言。然非论性之正也。告子所谓生之谓性。以知觉运动为性也。程子所谓生之谓性。善固性也而夹杂气则理亦有恶。夹杂说时性即气气即性。此与告子说语意自不同。幸更深考而细商焉。
为恶底物。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性。与此不同。性固是至善底。而及其气挟理而流于恶也。为恶者气而性亦随而为恶。故有是言。然非论性之正也。告子所谓生之谓性。以知觉运动为性也。程子所谓生之谓性。善固性也而夹杂气则理亦有恶。夹杂说时性即气气即性。此与告子说语意自不同。幸更深考而细商焉。答金武良(丙寅)
时光何其易也。此岁又暮矣。每念同志。为之耿耿。今奉手函。老怀良慰。第未骫年间所学长进否。大抵人生。朝青丝而暮白雪。少壮者不可不勉也。所询舜之怨自怨也。小弁之怨怨亲也。所怨不同。而小弁注言舜犹怨慕。若将以舜之怨为怨亲。是诚可疑也。虽然舜之怨小弁之怨。其不得于亲则一也。所以朱子发明小弁之无愆。而引孟子怨慕二字。而曰舜犹怨慕云尔。非谓舜之怨亦怨亲。学者于此不以辞害义可也。
答成舜直(耆德○甲子)
士之有相感。犹方响之应。贾子所谓同明相照。同气相求是也。衰朽之物。与世无闻。而每念时事。独有寡助之叹。不自意桑榆晚暮。幸得贤朋友之远访。清标高论。令人起懒。而不得久留良晤。此怀未可已也。继自今源源而相与。得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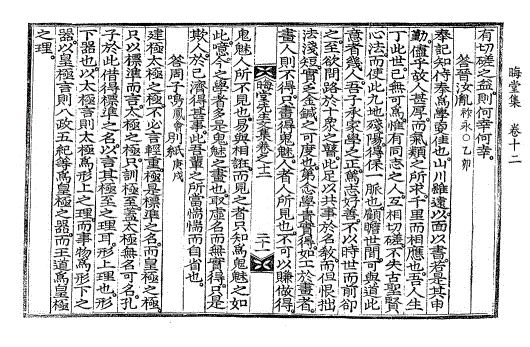 有切磋之益。则何幸何幸。
有切磋之益。则何幸何幸。答晋汝胤(祚永○乙卯)
奉记知侍奉为学更佳也。山川虽远。以面以书。若是其申勤。尽乎故人甚厚。而气类之所求。千里而相应也。吾人生丁此世。已无可为。惟有同志之人。互相切磋。不失古圣贤心法。而使此九地残阳。得保一脉也。顾瞻世间。可与道此意者几人。吾子承家学之正。笃志好善。不以时世而前却之。至欲问路于十象之瞽。此足以共事于名教。而但恨拙法浅短。实乏金针之可度也。第念学贵实得。如工于画者。画人则不得。只画得鬼魅。人者人所见也。不可以赚做得。鬼魅人所不见也。易与相诳。而见之者只知为鬼魅之如此。噫。今之学者多是鬼魅之画也。取虚名而无实得。只是欺人。于己济得甚事。此吾辈之所当惴惴而自省也。
答周子鸣(凤会)别纸(庚戌)
建极太极之极。不必言轻重。极是标准之名。而皇极之极。只以标准而言。太极之极。只训极至。盖太极无名可名。孔子于此借得标准之名。以言其极至之理耳。形上理也。形下器也。以太极言则太极为形上之理。而事物为形下之器。以皇极言则八政五纪等为皇极之器。而王道为皇极之理。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2L 页
 召诰郊祭。郊是祭天也。莫尊者其礼简。故只用牛。社则次之。故用太牢。率是以降。天子诸侯用太牢。牛羊豕是也。大夫用少牢。羊豕是也。士用特牲。豕是也。
召诰郊祭。郊是祭天也。莫尊者其礼简。故只用牛。社则次之。故用太牢。率是以降。天子诸侯用太牢。牛羊豕是也。大夫用少牢。羊豕是也。士用特牲。豕是也。论语性相近之性。是气质性也。孟子犬牛人之性。指本性也。孔孟之所主而言者不同。故集注所论。一则以兼气言。一则以本性言。然就犬牛人而各言其性则亦自不同。故朱子答程允夫书曰。天命之性则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只是指气质性。孟子所谓犬牛人之性殊者。指此而言。又答程正思曰。犬牛人之形气既异。则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异。告子一段。如此改定。但恐于一原处。未甚分明云云。盖尝言之。犬牛人莫不皆有本性。而平说犬牛人之性则是气质性也。但孟子方以所同之性。打破告子生之谓性。故其所指者在本性也。
三才之才。愚尝谓才材也。犹言材质也。天地人之形质具然后。始可曰天地人。故特言三才也。
大凡读书之法。思为贵。不思则疑不自生。疑不自生则亦末如之何已矣。必有疑然后。是乃进步处。有疑则可质于先进。若其疑不肯綮。而只以拣难为问者。反不如不问也。且凡学者必须大著心志。常常若擒龙搏虎然后。庶可有为。若夫志于小成者。亦何足道哉。试看今日世界。其可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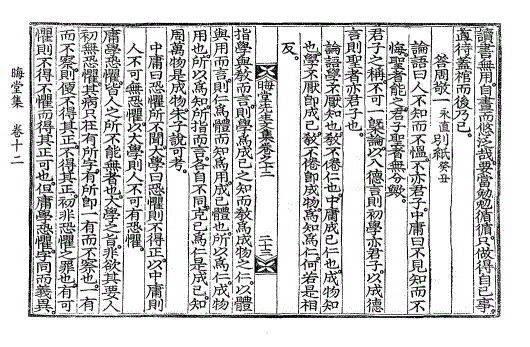 读书无用。自画而悠泛哉。要当勉勉循循。只做得自己事。直待盖棺而后乃已。
读书无用。自画而悠泛哉。要当勉勉循循。只做得自己事。直待盖棺而后乃已。答周敬一(永直)别纸(癸丑)
论语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中庸曰不见知而不悔。圣者能之。君子圣者无分欤。
君子之称。不可一槩论。以入德言则初学亦君子。以成德言则圣者亦君子也。
论语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学不厌即成己。教不倦即成物。为知为仁。何若是相反。
指学与教而言。则学为成己之知而教为成物之仁。以体与用而言。则仁为体而知为用。成己体也。所以为仁。成物用也。所以为知。所指而言。各自不同。克己为仁是成己。知周万物是成物。朱子说可考。
中庸曰恐惧所不闻。大学曰恐惧则不得正。以中庸则人不可无恐惧。以大学则人不可有恐惧。
庸学恐惧。皆人之所不能无者也。大学之旨。非欲其要人初无恐惧。其病只在有所字。有所即一有而不察也。一有而不察。则便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初非恐惧之罪也。有可惧则不得不惧而得其正可也。但庸学恐惧。字同而义异。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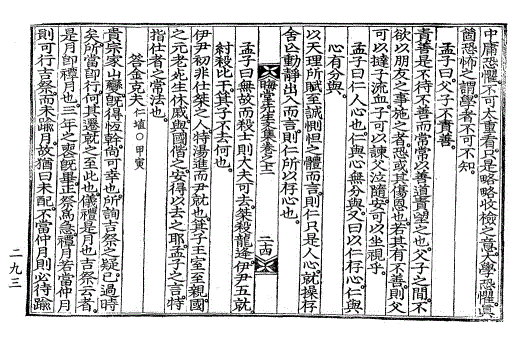 中庸恐惧。不可太重看。只是略略收检之意。大学恐惧。真个恐怖之谓。学者不可不知。
中庸恐惧。不可太重看。只是略略收检之意。大学恐惧。真个恐怖之谓。学者不可不知。孟子曰。父子不责善。
责善是不待不善而常常以善道责望之也。父子之间。不欲以朋友之事施之者。恐或其伤恩也。若其有不善。则父可以挞子流血。子可以谏父泣随。安可以坐视乎。
孟子曰仁人心也。仁与心无分与。又曰以仁存心。仁与心有分与。
以天理所赋至诚恻怛之体而言。则仁只是人心。就操存舍亡动静出入而言。则仁所以存心也。
孟子曰无故而杀士则大夫可去。桀杀龙逢。伊尹五就。纣杀比干。箕子不去何也。
伊尹初非仕桀之人。特汤进而尹就也。箕子王室至亲。国之元老死生休戚。与国偕之。安得以去之耶。孟子之言。特指仕者之常法也。
答金克夫(仁埴○甲寅)
贵宗家山变。既得恒干。尚可幸也。所询吉祭之疑。已过时矣。所当即行。何其迁就之至此也。仪礼是月也吉祭云者。是月即禫月也。三年之丧既毕。正祭为急。禫月若当仲月则可行吉祭。而未踰月。故犹曰未配。不当仲月则必待踰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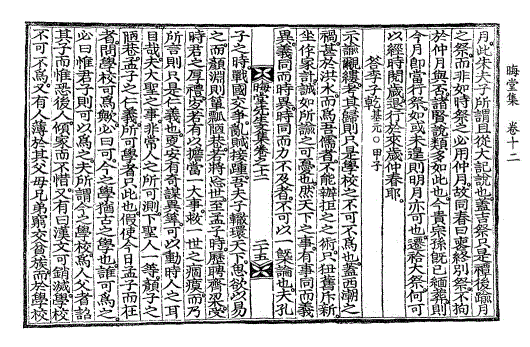 月。此朱夫子所谓且从大记说也。盖吉祭只是禫后踰月之祭。而非如时祭之必用仲月。故同春曰丧终别祭。不拘于仲月与否。诸贤说类多如此也。今贵宗孙既已缅葬。则今月即当行祭。如或未遑则明月亦可也。迁祫大祭。何可以经时阅岁。退行于来岁仲春耶。
月。此朱夫子所谓且从大记说也。盖吉祭只是禫后踰月之祭。而非如时祭之必用仲月。故同春曰丧终别祭。不拘于仲月与否。诸贤说类多如此也。今贵宗孙既已缅葬。则今月即当行祭。如或未遑则明月亦可也。迁祫大祭。何可以经时阅岁。退行于来岁仲春耶。答李子乾(基元○甲子)
示谕覼缕。考其归则只是学校之不可不为也。盖西潮之祸。甚于洪水。而为吾儒者。不能办拒之之术。只狃旧斥新。坐作家计。诚如所谕之可忧也。然天下之事。有事同而义异。义同而时异。时同而力不及者。不可以一槩论也。夫孔子之时。战国交争。乱贼接踵。吾夫子辙环天下。思欲以易之。而颜渊则箪瓢陋巷。若将忘世。至孟子时。历聘齐梁。受时君之厚礼。宜若有以担当一大事。救一世之痼瘼。而乃所言则只是仁义也。更安有奇谋异算。可以动时人之耳目哉。夫大圣之事。非常人之所可测。下圣人一等。颜子之陋巷。孟子之仁义。所可学者只此也。假使今日孟子而在者。问学校可为欤。必曰可。今之学犹古之学也。谁可为之。必曰惟君子则可以为之。夫所谓今之学校。为人父者诏其子而惟恐后人。倾家而不惜。又有曰汉文可销灭。学校不可不为。又有人薄于其父母兄弟穷交贫族。而于学校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4L 页
 则资人钜赀。自要其名誉而陷人于坎阱。是数者毕竟成就得讥孔孟去父母。父子自由。男女平等。女择配男公妻之学。下焉者败其家而亡其躯。上焉者不过为他人之鹰犬。呜呼。是岂常情之所可知耶。居今之世。亦自有时措之宜。老谬之见。每常曰随所在而各立学校。外借学校之名。而益读圣贤之书。益笃伦常之教。兼时务之最要者一二科。又择其有俊秀者。兼治武经。如此则尚可以达权通变而养成人材也。往在北塞。与尊先公约定此意。将欲设教于云斋而所不谐者。乃君辈之因其事而幻脱之。欲使祖云一区。遂成一个新学校也。可胜叹哉。其后几年。君辱于寿春而无所做得。又设校于本洞而所做者又何事。坐算来头之事。老夫之守拙无用。君之用力有为。一般是无所做得。而遂失故家物色。幻却先人论议。则君之兄弟恐输了老夫一著矣。可不戒哉。呜呼。先君子乃吾党中有为之材也。以正大之学。有达权之材。其苦心于天下事。岂君辈比哉。天不憖遗。人事异昔。君辈只得谨守先人之业。庶几寡过。无获罪于圣人之门可也。乃若损益于殷周之礼。通变于大易之道。挽回此世之教。则君辈无先公之学。又无先公之材。而徒欲有为于斯世。则此如卖薪者之终日唱盐而无所售矣。今日世道至此。虽有先公之学术才局。胸
则资人钜赀。自要其名誉而陷人于坎阱。是数者毕竟成就得讥孔孟去父母。父子自由。男女平等。女择配男公妻之学。下焉者败其家而亡其躯。上焉者不过为他人之鹰犬。呜呼。是岂常情之所可知耶。居今之世。亦自有时措之宜。老谬之见。每常曰随所在而各立学校。外借学校之名。而益读圣贤之书。益笃伦常之教。兼时务之最要者一二科。又择其有俊秀者。兼治武经。如此则尚可以达权通变而养成人材也。往在北塞。与尊先公约定此意。将欲设教于云斋而所不谐者。乃君辈之因其事而幻脱之。欲使祖云一区。遂成一个新学校也。可胜叹哉。其后几年。君辱于寿春而无所做得。又设校于本洞而所做者又何事。坐算来头之事。老夫之守拙无用。君之用力有为。一般是无所做得。而遂失故家物色。幻却先人论议。则君之兄弟恐输了老夫一著矣。可不戒哉。呜呼。先君子乃吾党中有为之材也。以正大之学。有达权之材。其苦心于天下事。岂君辈比哉。天不憖遗。人事异昔。君辈只得谨守先人之业。庶几寡过。无获罪于圣人之门可也。乃若损益于殷周之礼。通变于大易之道。挽回此世之教。则君辈无先公之学。又无先公之材。而徒欲有为于斯世。则此如卖薪者之终日唱盐而无所售矣。今日世道至此。虽有先公之学术才局。胸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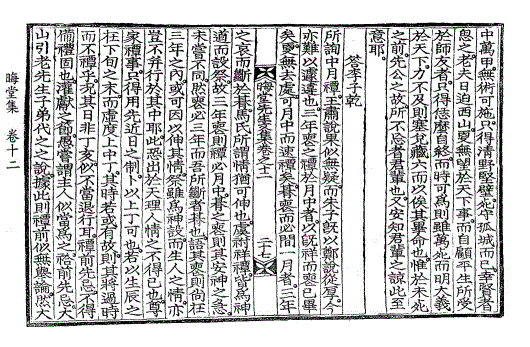 中万甲。无术可施。只得清野坚壁。死守孤城而已。幸贤者思之。老夫日迫西山。更无望于天下事。而自顾平生所受于师友者。只得恁么自终。而时可为则虽万死而明大义于天下。力不及则塞兑藏六而以俟其毕命也。惟于未死之前。先公之故。所不忘者君辈也。又安知君辈之谅此至意耶。
中万甲。无术可施。只得清野坚壁。死守孤城而已。幸贤者思之。老夫日迫西山。更无望于天下事。而自顾平生所受于师友者。只得恁么自终。而时可为则虽万死而明大义于天下。力不及则塞兑藏六而以俟其毕命也。惟于未死之前。先公之故。所不忘者君辈也。又安知君辈之谅此至意耶。答李子乾
所询中月禫。王肃说果似无疑。而朱子既以郑说从厚。今亦难以遽违也。三年丧之禫于月中者。以既祥而丧已毕矣。更无去处。可月中而速禫矣。期丧而必间一月者。三年之哀而断于期。马氏所谓情犹可伸也。虞祔祥禫。皆为神道而设祭。故三年丧则禫必月中。期之丧则其安神之急。未尝不同。然丧必三年而吾所断者期也。语其丧则尚在三年之内。或可因以伸其情。祭虽为神设。而生人之情。亦岂不并行于其中耶。此恐出于天理人情之不得已也。尊家禫事。只得用先近日之制。卜以上丁可也。若以生辰之在下旬之末。而虚度上中丁。其时若或有故。则其将过时而不禫乎。况其日非丁亥。似不当退行耳。禫前先忌。不得备礼固也。灌献之节。愚尝谓主人似当为之。祫前先忌。大山引老先生子弟代之之说。据此则禫前似无举论。然大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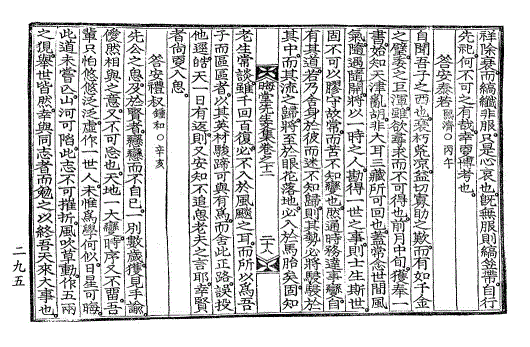 祥除衰。而缟纤非服。只是心哀也。既无服则缟笠带。自行先祀。何不可之有哉。幸更博考也。
祥除衰。而缟纤非服。只是心哀也。既无服则缟笠带。自行先祀。何不可之有哉。幸更博考也。答安泰若(熙济○丙午)
自闻吾子之西也。衰朽荒凉。益切寡助之叹。而有如千金之璧。委之巨浑。虽欲寻求而不可得也。前月中旬。获奉一书。始知天津乱胡。非大耳三藏所可回也。盖常念世间风气。随遇随开。将以一时之人。勘得一世之事。则士生斯世。固不可以胶守故常。而苦不知变也。然通时务达事变。自有其道。若乃舍身于彼而迷不知归。则其势必将骎骎于其中。而其流之归。将至于眼花落地。必入于马胎矣。固知老生常谈。虽千回百复。必不入于风飙之耳。而所以为吾子而区区者。以其英材骏蹄可与有为。而舍此正路。误投他径。皓天一日有返。则又安知不追思老夫之言耶。幸贤者尚更入思。
答安礼叔(钟和○辛亥)
先公之思。及于贤者。恋恋而不自已。一别数岁。获见手谕。僾然相与之意。又不可忘也。天地一大变。时序又不留。吾辈只怕悠悠泛泛。虚作一世人。未惟为学何似。日星可晦。此道未尝亡。山河可陷。此志不可摧折。风吹草动。作五两之𤞭。举世皆然。幸与同志者而勉之以终吾天来大事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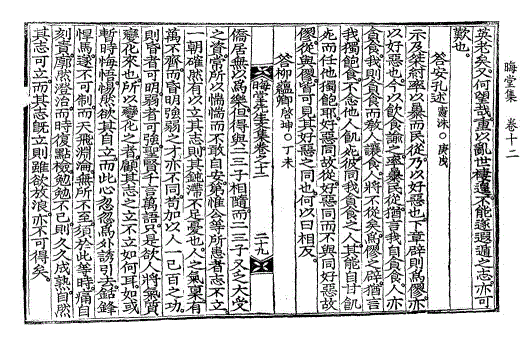 英老矣。又何望哉。重以乱世栖遑。不能遂遐遁之志。亦可叹也。
英老矣。又何望哉。重以乱世栖遑。不能遂遐遁之志。亦可叹也。答安孔述(宪洙○庚戌)
示及桀纣率以㬥而民从。乃以好恶也。下章辟则为僇。亦以好恶也。今以饮食谕之。率㬥民从。犹言我自贪食。人亦贪食。我则贪食而教人让食。人将不从矣。为僇之辟。犹言我独饱食。不念他人饥死。彼同我贪食之人。其能自甘饥死而任他独饱耶。好恶同故从。好恶同而不与同好恶故僇。从与僇。皆可见其好恶之同也。何以曰相反。
答柳蕴卿(启坤○丁未)
侨居无以为乐。但得与二三子相随。而二三子又乏大受之资。常所以惴惴而不敢自安。第惟公等所患者志不立。一朝确然有以立其志。则其钝滞不足忧也。人之气禀。有万不齐。而昏明强弱之才亦不同。苟加以人一己百之功。则昏者可明。弱者可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气质变化来也。所以变化之者。顾其志之立不立如何耳。如或暂时悔悟。惕然欲其自立。而此心忽忽为外诱引去。铦锋悍马。遂不可制。而天飞渊沦。无所不至。须于此等时。痛自刻责。廓然澄治。而时复点检。勉勉不已。则久久成熟。自然其志可立。而其志既立则虽欲放浪。亦不可得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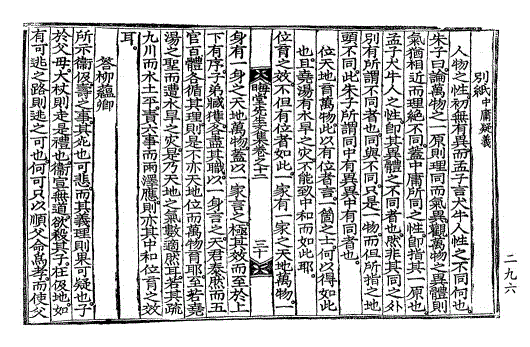 别纸(中庸疑义)
别纸(中庸疑义)人物之性。初无有异。而孟子言犬牛人性之不同何也。
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盖中庸所同之性。即指其一原也。孟子犬牛人之性。即其异体之不同者也。然非其同之外别有所谓不同者也。同与不同。只是一物。而但所指之地头不同。此朱子所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者也。
位天地育万物。此以有位者言。一个之士。何以得如此也。且尧汤有水旱之灾。不能致中和而如此耶。
位育之效。不但有位者如此。一家有一家之天地万物。一身有一身之天地万物。盖以一家言之。极其效而至于上下有序。子弟臧获。各尽其职。以一身言之。天君泰然而五官百体各循其理。则是不亦天地位而万物育耶。至若尧汤之圣而遭水旱之灾。是乃天地之气数适然耳。若其疏九川而水土平。责六事而雨泽应。则亦其中和位育之效耳。
答柳蕴卿
所示卫伋,寿之事。其死也可悲。而其义理则果可疑也。子于父母。大杖则走是礼也。卫宣无道。欲杀其子。在伋地。如有可逃之路则逃之可也。何可只以顺父命为孝。而使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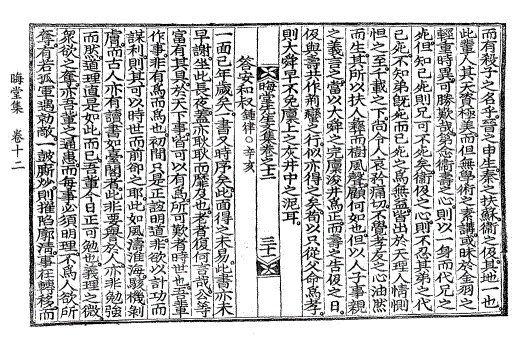 而有杀子之名乎。晋之申生。秦之扶苏。卫之伋。其地一也。此辈人其天资极美。而但无学术之素讲。或昧于金羽之轻重时异。可胜叹哉。第念卫寿之心。则以一身而代兄之死。但知己死则兄可不死矣。卫伋之心。则不忍其弟之代己死。不知弟既死而己死之为无益。皆出于天理人情恻怛之至。千载之下。尚令人哀矜痛切。不觉孝友之心油然而生。其所以扶人彝而树风声。顾何如也。但以人子事亲之义言之。当以大舜之完廪浚井为正。而寿之告伋之日。伋与寿共作荆蛮之行。似亦得之矣。苟以只从父命为孝。则大舜早不免廪上之灰井中之泥耳。
而有杀子之名乎。晋之申生。秦之扶苏。卫之伋。其地一也。此辈人其天资极美。而但无学术之素讲。或昧于金羽之轻重时异。可胜叹哉。第念卫寿之心。则以一身而代兄之死。但知己死则兄可不死矣。卫伋之心。则不忍其弟之代己死。不知弟既死而己死之为无益。皆出于天理人情恻怛之至。千载之下。尚令人哀矜痛切。不觉孝友之心油然而生。其所以扶人彝而树风声。顾何如也。但以人子事亲之义言之。当以大舜之完廪浚井为正。而寿之告伋之日。伋与寿共作荆蛮之行。似亦得之矣。苟以只从父命为孝。则大舜早不免廪上之灰井中之泥耳。答安和叔(钟律○辛亥)
一面已年岁矣。一书又时序矣。此面得之未易。此书亦未早谢。坐此长夜。盖亦耿耿而靡及也。老者复何言哉。公等富有其具。于天下事。皆可以有为。所可叹者时世也。吾辈作事。非有为而为也。初间只是正谊明道。非欲以计功而谋利。则其可以时世而前却之耶。此如风涛淮海。骇机剥肤。而古人亦有读书如台阁者。此非要誉于人。亦非勉强而然。道理直是如此而已。吾辈今日正可勉也。义理之微。众欲之夺。亦吾辈之通患。而每事必须明理。不为人欲所夺。有若孤军遇勍敌。一鼓厮炒。则摧陷廓清。事在转移。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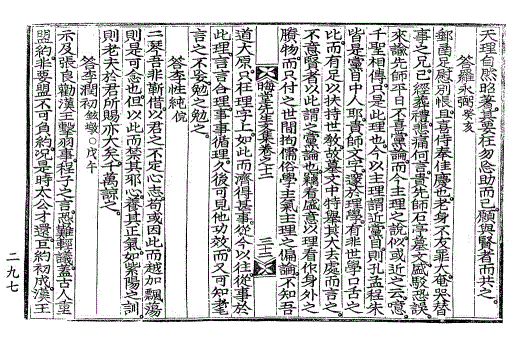 天理自然昭著。其要在勿忘助而已。愿与贤者而共之。
天理自然昭著。其要在勿忘助而已。愿与贤者而共之。答罗永弼(癸亥)
邮函足慰别怅。且喜侍奉佳庆也。老身不友罪大。奄哭替事之兄。已经葬礼。悲痛何言。贵先师石亭墓文。盛驳恐误。来谕先师平日不喜党论。而今主理之说。似或近之云。噫。千圣相传。只是此理也。今以主理谓近党目。则孔孟程朱皆是党目中人耶。贵师文字。邃于理学。有非世学口舌之比。而有足以扶持世教。故墓文中特举其大去处而言之。不意贤者以此谓之党论也。窃看盛意以理看作身外之剩物。而只付之世间拘儒俗学主气主理之偏论。不知吾道大原。只在理字上。如此而济得甚事。从今以往。从事于此理。言言合理。事事循理。久后可见他功效。而又可知耄言之不妄。勉之勉之。
答李性纯 俒○甲辰(저본에는 없다. 저본의 원목차에 근거하여 보충하였다.)
二琴吾非靳借。以君之不定心志。苟或因此而越加飘荡则是可念也。但以此而禁其邪心。养其正气。如紫阳之训。则老夫于君所赐亦大矣。千万谅之。
答李润初(铉墩○戊午)
示及张良劝汉王击羽事。程子之言。恐难轻议。盖古人重盟约。非要盟不可负约。况是时太公才还。巨约初成。汉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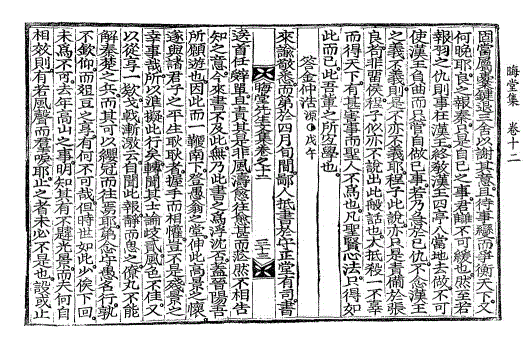 固当属櫜键退三舍以谢其意。且待事变而争衡天下。又何晚耶。良之报秦。只是自己之事。君雠不可缓也。然至若报羽之仇则事在汉王。终教汉王四亭八当地去做。不可使汉王负曲而只管自做己事。若乃急于己仇。不念汉王之义不义。则是不亦不义耶。程子此说。亦只是责备于张良。苟非留侯。程子似亦不说出此般话也。大抵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甚害事而圣人不为也。凡圣贤心法。只得如此而已。此吾辈之所宜学也。
固当属櫜键退三舍以谢其意。且待事变而争衡天下。又何晚耶。良之报秦。只是自己之事。君雠不可缓也。然至若报羽之仇则事在汉王。终教汉王四亭八当地去做。不可使汉王负曲而只管自做己事。若乃急于己仇。不念汉王之义不义。则是不亦不义耶。程子此说。亦只是责备于张良。苟非留侯。程子似亦不说出此般话也。大抵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甚害事而圣人不为也。凡圣贤心法。只得如此而已。此吾辈之所宜学也。答金仲浩(源○戊午)
来谕敬悉。而第于四月旬间。鄙人抵书于守正堂有司。书送首任辞单。且责其是非风涛愈往愈甚而茫然不相告知之意。今来书不及此。无乃此书之为浮沈否。盖晋阳吾所愿游也。因此而一鞭南下。登愚翁之堂。伸此高景之怀。遂与诸君子之平生耿耿者。握手而相欢。岂不是残景之幸事哉。所以准拟此行矣。转闻其士论歧贰。风色不佳。又以从享一款。戈戟渐激云。自闻此报。静而思之。僚丸不能解秦楚之兵。而其可以缨冠而往焉耶。第念守愚名行。孰不钦仰。而俎豆之享。有何不可哉。但时世如此。少俟下回。未为不可。去年高山之事。明知其有不韪光景。而夫何自相效则。有若风声而群唳耶。止之者未必不是也。设或止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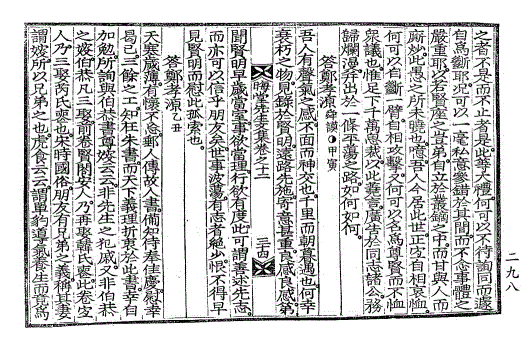 之者不是而不止者是。此等大礼。何可以不待询同而遽自为断耶。况可以一毫私意参错于其间。而不念事体之严重耶。以若贤座之岂弟。自立于丛镝之中。而甘与人而厮炒。此愚之所未晓也。噫。吾人今居此世。正宜自相哀恤。何可以自断一臂。自相攻击。又何可以名为尊贤而不恤众议也。惟足下千万思裁。以此荛言。广告于同志诸公。务归烂漫。并出于一条平荡之路。如何如何。
之者不是而不止者是。此等大礼。何可以不待询同而遽自为断耶。况可以一毫私意参错于其间。而不念事体之严重耶。以若贤座之岂弟。自立于丛镝之中。而甘与人而厮炒。此愚之所未晓也。噫。吾人今居此世。正宜自相哀恤。何可以自断一臂。自相攻击。又何可以名为尊贤而不恤众议也。惟足下千万思裁。以此荛言。广告于同志诸公。务归烂漫。并出于一条平荡之路。如何如何。答郑孝源(舜谟○甲寅)
吾人有声气之感。不面而神交也。千里而朝暮遇也。何幸衰朽之物。见录于贤明。远路先施。寄意甚重。良感良感。第闻贤明早岁当室。事欲当理。行欲有度。此可谓善述先志。而亦可以信乎朋友矣。世事波荡。有志者绝少。恨不得早见贤明而慰此孤索也。
答郑孝源(乙丑)
天寒岁薄。有怀不忘。邮人传故人书。备知侍奉佳庆。慰幸曷已。三馀之工。知在朱书。而天下义理折衷于此书。幸自加勉。所询与伯恭书尊嫂云云。非先生之犯戚。又非伯恭之嫂。伯恭凡三娶。前卷贤閤安人。乃再娶韩氏丧。此卷宜人。乃三娶芮氏丧也。宋时国俗。朋友有兄弟之义。称其妻谓嫂。所以兄弟之也。虎食云云。谓单豹导气养生而竟为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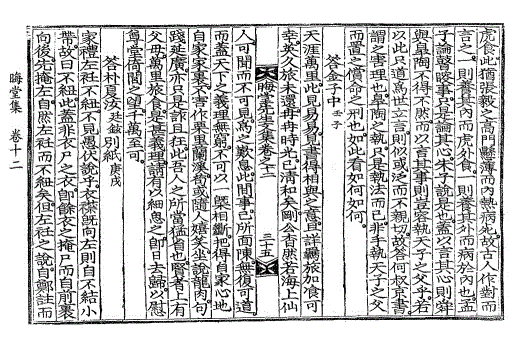 虎食。此犹张毅之高门悬薄而内热病死。故古人作对而言之。一则养其内而虎外食。一则养其外而病于内也。孟子论瞽瞍事。只是论其心。朱子说是也。盖以言其心则舜与皋陶不得不然。而以言其事则岂容执天子之父乎。若以此只道为世立言。则似或泛而不亲切。故答何叔京书。谓之害理也。皋陶之执。只是执法而已。非手执天子之父而置之偿命之刑也。如此看如何如何。
虎食。此犹张毅之高门悬薄而内热病死。故古人作对而言之。一则养其内而虎外食。一则养其外而病于内也。孟子论瞽瞍事。只是论其心。朱子说是也。盖以言其心则舜与皋陶不得不然。而以言其事则岂容执天子之父乎。若以此只道为世立言。则似或泛而不亲切。故答何叔京书。谓之害理也。皋陶之执。只是执法而已。非手执天子之父而置之偿命之刑也。如此看如何如何。答金子中(壬子)
天涯万里。此见易易。见书得相与之意。且详羁旅加餐可幸。英久旅未还。冉冉时光。已清和矣。刚公杳然若海上仙人。可闻而不可见。为之叹息。此间事。已所面陈。无复可道。而盖天下之义理无穷。不可以一槩相断。把得自家心地自家家里。不害作栗里兰溪。苟或随人嬉笑。坐说龙肉。句践延广。亦只是诈且狂。此吾人之所当猛省也。贤者上有父母。万里旅食。是甚义理。请有以细思之。即日去归。以慰尊堂倚闾之望。千万至可。
答朴夏汝(廷铉)别纸(庚戌)
家礼左衽不纽。不见愚伏说乎。衣襟既向左则自不结小带。故曰不纽。此盖非衣尸之衣。即馀衣之掩尸而自前裹向后。先掩左。自然左衽而不纽矣。但左衽之说。自郑注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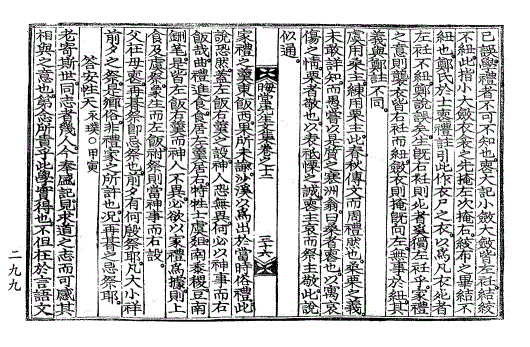 已误。学礼者不可不知也。丧大记小敛大敛皆左衽。结绞不纽。此指小大敛衣衾之先掩左次掩右。绞布之毕结不纽也。郑氏于士丧礼注引此作衣尸之衣。以为凡衣死者左衽不纽。郑说误矣。生既右衽则死者奚独左衽乎。家礼之意则袭衣皆右衽而纽。敛衣则掩既向左。无事于纽。其义与郑注不同。
已误。学礼者不可不知也。丧大记小敛大敛皆左衽。结绞不纽。此指小大敛衣衾之先掩左次掩右。绞布之毕结不纽也。郑氏于士丧礼注引此作衣尸之衣。以为凡衣死者左衽不纽。郑说误矣。生既右衽则死者奚独左衽乎。家礼之意则袭衣皆右衽而纽。敛衣则掩既向左。无事于纽。其义与郑注不同。虞用桑主。练用栗主。此春秋传文而周礼然也。桑栗之义。未敢详知。而愚尝以是质之寒洲翁。曰桑者丧也。以寓哀伤之情。栗者敬也。以表祗慄之诚。丧主哀而祭主敬。此说似通。
家礼之羹东饭西。果所未谕。沙溪以为出于当时俗礼。此说恐然。盖左饭右羹之设。神人恐无异。何必以神事而右饭哉。曲礼进食。食居左羹居右。特牲士虞。俎南黍稷。豆南铏芼。是皆左饭右羹而神人不异。必欲以家礼为据。则上食及虞祭。象生而左饭。祔祭则当神事而右设。
父在母丧。再期祭即忌祭也。前夕有何殷祭耶。凡大小祥前夕之祭。是乡俗。非礼家之所许也。况再期之忌祭耶。
答安性天(永璞○甲寅)
老寄斯世。同志者几人。今奉盛记。见求道之志而可感其相与之意也。第念所责乎此学实得也。不但在于言语文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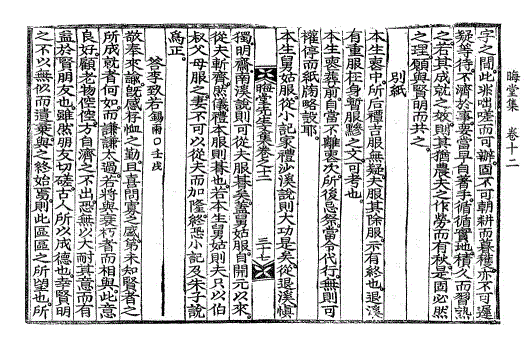 字之间。此非咄嗟而可办。固不可朝耕而暮穫。亦不可迟疑等待。不济于事。要当早自著手。循循实地。积久而习熟之。若其成就之效。则其犹农夫之作劳而有秋。是固必然之理。愿与贤明而共之。
字之间。此非咄嗟而可办。固不可朝耕而暮穫。亦不可迟疑等待。不济于事。要当早自著手。循循实地。积久而习熟之。若其成就之效。则其犹农夫之作劳而有秋。是固必然之理。愿与贤明而共之。别纸
本生丧中。所后禫吉服无疑。夫服其除服。示有终也。退溪有重服在身暂服黪之文。可考也。
本生丧葬前。自当不离丧次。所后忌祭。当令代行。无则可权停而纸榜略设耶。
本生舅姑服。从小记家礼沙溪说则大功是矣。从退溪,慎独,明斋,南溪说则可从夫服期矣。盖舅姑服。自开元以来。从夫斩齐。然仪礼本服则期也。若本生舅姑则夫只以伯叔父母服之。妻不可以从夫而加隆。终恐小记及朱子说为正。
答李致若(锡雨○壬戌)
敬奉来谕。既感存恤之勤。且喜问寡之盛。第未知贤者之所成就者何如。而谦谦太过。若将与衰朽者而相与。此意良好。顾老物倥倥。方自济之不出。恐无以大耐其意而有益于贤朋友也。虽然朋友切磋。古人所以成德也。幸贤明之不以无似而遗弃。与之终始焉。则此区区之所望也。所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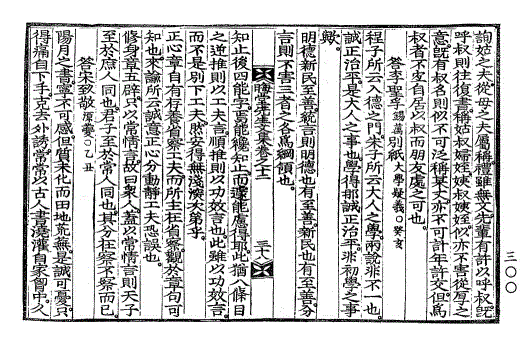 询姑之夫,从母之夫属称。礼虽无文。先辈有许以呼叔。既呼叔则往复书。称姑叔妇侄,姨叔姨侄。似亦不害从厚之意。既有叔名则似不可泛称某丈。亦不可计年许交。但为叔者不宜自居以叔而朋友处之可也。
询姑之夫,从母之夫属称。礼虽无文。先辈有许以呼叔。既呼叔则往复书。称姑叔妇侄,姨叔姨侄。似亦不害从厚之意。既有叔名则似不可泛称某丈。亦不可计年许交。但为叔者不宜自居以叔而朋友处之可也。答李圣孚(锡万)别纸(大学疑义○癸亥)
程子所云入德之门。朱子所云大人之学。两说非不一也。诚正治平。是大人之事也。学得那诚正治平。非初学之事欤。
明德新民至善。统言则明德也有至善。新民也有至善。分言则不害三者之各为纲领也。
知止后四能字。焉能才知止。而遽能虑得耶。此犹八条目之逆推则以工夫言。顺推则以功效言也。此虽以功效言。而不是别下工夫。然安得无浅深次第乎。
正心章自有存养省察工夫。而所主在省察。观于章句可知也。来谕所云诚意正心分动静工夫恐误也。
修身章五辟。只以常情言。故曰众人。盖以常情言则天子至于庶人同也。君子至于常人同也。其分在察不察而已。
答宋致敬(源夔○乙丑)
阳月之书。宁不可感。但质未化而田地荒芜。是诚可忧。只得痛自下手。克去外诱。常常以古人书浇灌自家胸中。久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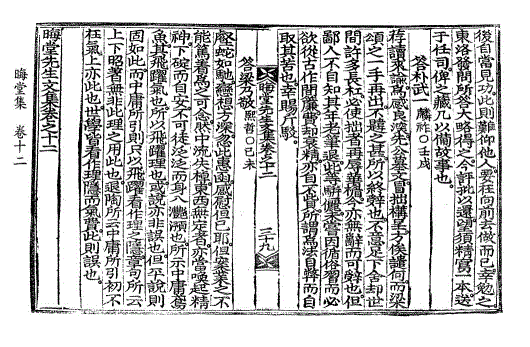 后自当见功。此则难仰他人。要在向前去做而已。幸勉之。东洛发问所答大略得之。今评批以还。望须精写一本。送于任司。俾之藏几以备故事也。
后自当见功。此则难仰他人。要在向前去做而已。幸勉之。东洛发问所答大略得之。今评批以还。望须精写一本。送于任司。俾之藏几以备故事也。答朴武一(麟祚○壬戌)
荐读来谕。为感良深。先公墓文。冒拙构呈。方俟谴何。而梁颂之一手再出。不韪之甚。所以终辞也。不意足下舍却世间许多长杠。必使拙者再辱华楣。今亦无辞而可辞也。但鄙人不自知其年老笔退。此等骈俪。未尝因循俗习而必欲从古作间帘。费却衰精。亦自不赀。所谓为法自弊而自取其苦也。幸赐斤驳。
答梁乃敬(熙哲○己未)
壑蛇如驰。恋想方深。忽此惠函。感慰但已耶。但案业之不能笃着为之可念。然中流失棹。东西无定者。亦当唤起精神。下碇而自安。不可徒泛泛而身入滟滪也。所示中庸鸢鱼。其飞跃气也。所以飞跃理也。或说亦非误也。但平说则固如此。而中庸所引则只以飞跃看作理之隐。章句所云上下昭著无非此理之用此也。退陶所云中庸所引初不在气上亦此也。世学皆看作理隐而气费。此则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