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书
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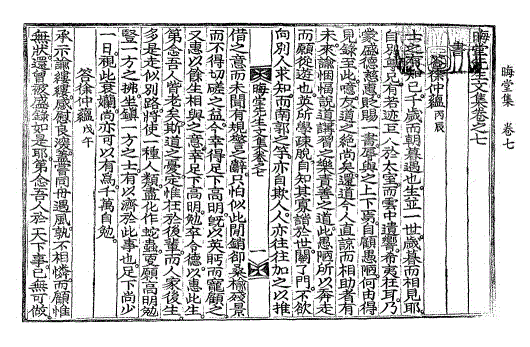 答徐仲蕴(丙辰)
答徐仲蕴(丙辰)士之有知己。千岁而朝暮遇也。生并一世。岁暮而相见耶。自别尊兄。有若迹巨人于太室。而云中遗响。希夷在耳。乃蒙盛德慈惠。贬赐一书。辱与之上下焉。自顾愚陋。何由得见录至此。噫。友道之绝尚矣。还道今人直谅而相助者有未。来谕悃愊说道讲习之乐责善之道。此愚陋所以奔走而愿从游也。英所学疏脱。自知其寡谐于世。关了门。不欲向别人求知。而南郭之竽。亦自欺人。人亦往往加之以推借之意而未闻有规警之辞。只怕似此閒销却桑榆残景而不得切磋之益。今幸得足下高明。既以英眄而宠顾之。又惠以馀生相与之意。幸足下高明。勉卒令德。以惠此生。第念吾人皆老矣。斯道之忧。定惟在于后辈。而人家后生。多是走似别路。将使一种人类。尽化作蛇虫。更愿高明勉竖一方之拂。坐镇一方之士。有以济于此事也。足下尚少一日。视此衰懒。尚亦可以有为。千万自勉。
答徐仲蕴(戊午)
承示谕缕缕。感慰良深。盖尝同舟遇风。孰不相怜。而顾惟无状。还曾被盛录如是耶。第念吾人于天下事。已无可做。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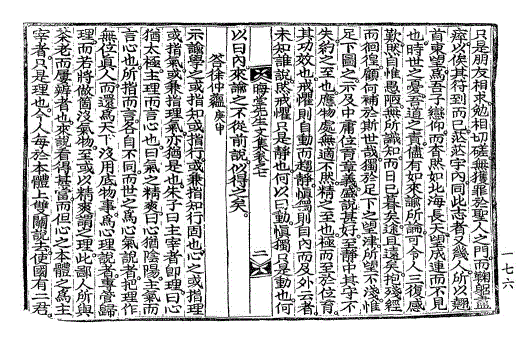 只是朋友相求。勉相切磋。无获罪于圣人之门。而鞠躬尽瘁。以俟其符到而已。茫茫宇内。同此志者又几人。所以翘首东望。为吾子恋仰。而杳然如北海长天。望成连而不见也。时世之忧。吾道之责。尽有如来谕所论。可令人三复感叹。然自惟愚陋。无所识知。而日已暮矣。途且远矣。抱残经而徊徨。顾何补于斯世哉。独于足下之望津。所望不浅。惟足下图之。示及中庸位育章义。盛说甚好。至静中其守不失。约之至也。应物处无适不然。精之至也。极而至于位育。其功效也。戒惧则自动而趋静。慎独则自内而及外云者。未知谁说。然戒惧只是静也。何以曰动。慎独只是动也。何以曰内。来谕之不从前说。似得之矣。
只是朋友相求。勉相切磋。无获罪于圣人之门。而鞠躬尽瘁。以俟其符到而已。茫茫宇内。同此志者又几人。所以翘首东望。为吾子恋仰。而杳然如北海长天。望成连而不见也。时世之忧。吾道之责。尽有如来谕所论。可令人三复感叹。然自惟愚陋。无所识知。而日已暮矣。途且远矣。抱残经而徊徨。顾何补于斯世哉。独于足下之望津。所望不浅。惟足下图之。示及中庸位育章义。盛说甚好。至静中其守不失。约之至也。应物处无适不然。精之至也。极而至于位育。其功效也。戒惧则自动而趋静。慎独则自内而及外云者。未知谁说。然戒惧只是静也。何以曰动。慎独只是动也。何以曰内。来谕之不从前说。似得之矣。答徐仲蕴(庚申)
示谕学之或指知或指行。或兼指知行固也。心之或指理或指气。或兼指理气。亦犹是也。朱子曰主宰者即理。曰心犹太极。主理而言心也。曰气之精爽。曰心犹阴阳。主气而言心也。所指而言。各自不同。而世之为心气说者。把理作无位真人。而还为天下没用底物事。为心理说者。专管归理。而若将做个没气物。至或以精爽谓之理。此鄙人所与茶老而屡辨者也。来说看得甚当。而但心之本体之为主宰者。只是理也。今人每于本体上双关说去。使国有二君。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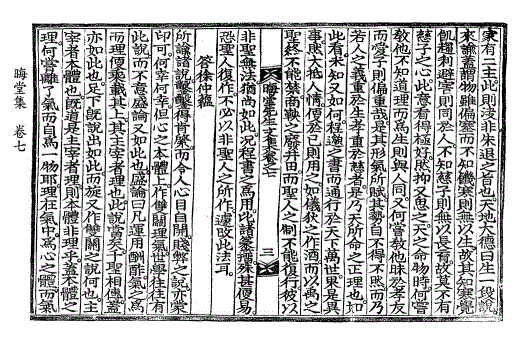 家有二主。此则决非朱退之旨也。天地大德曰生一段说。来谕盖谓物虽偏塞而不知饥寒则无以生。故其知寒觉饥趋利避害则同于人。不知慈子则无以长育。故莫不有慈子之心。此意看得极好。然抑又思之。天之命物时。何尝教他不知道理而为生则与人同。又何尝教他昧于孝友而爱子则偏重哉。是其形气所赋。其势自不得不然。而乃若人之义重于生孝重于慈者。是乃天所命之正理也。如此看。未知又如何。程邈之书而通行于天下万世。果是异事。然大抵人情。便于己则用之。如仪狄之作酒。而以禹之圣终不能禁。商鞅之废井田。而圣人之制不能复行。彼以非圣无法。犹尚如此。况程书之为用。比诸篆籀。殊甚便易。恐圣人复作。不必以非圣人之所作。遽改此法耳。
家有二主。此则决非朱退之旨也。天地大德曰生一段说。来谕盖谓物虽偏塞而不知饥寒则无以生。故其知寒觉饥趋利避害则同于人。不知慈子则无以长育。故莫不有慈子之心。此意看得极好。然抑又思之。天之命物时。何尝教他不知道理而为生则与人同。又何尝教他昧于孝友而爱子则偏重哉。是其形气所赋。其势自不得不然。而乃若人之义重于生孝重于慈者。是乃天所命之正理也。如此看。未知又如何。程邈之书而通行于天下万世。果是异事。然大抵人情。便于己则用之。如仪狄之作酒。而以禹之圣终不能禁。商鞅之废井田。而圣人之制不能复行。彼以非圣无法。犹尚如此。况程书之为用。比诸篆籀。殊甚便易。恐圣人复作。不必以非圣人之所作。遽改此法耳。答徐仲蕴
所谕诸说。凿凿得肯綮。而令人心目自开。贱弊之说。亦蒙印可。何幸何幸。但心之本体上。作双关理气。世学往往有此说。而不意盛论又如此也。盛论曰凡运用酬酢。气之为而理便乘载其上。其主宰者理也。此说当矣。千圣相传。盖亦如此也。足下既说出如此。而旋又作双关之说何也。主宰者本体也。既道是主宰者理。则本体非理乎。盖本体之理。何尝离了气而自为一物耶。理在气中。为心之体。而气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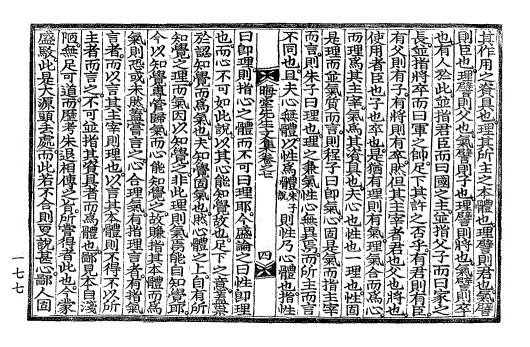 其作用之资具也。理其所主之本体也。理譬则君也。气譬则臣也。理譬则父也。气譬则子也。理譬则将也。气譬则卒也。有人于此。并指君臣而曰国之主。并指父子而曰家之长。并指将卒而曰军之帅。足下其许之否乎。有君则有臣。有父则有子。有将则有卒。然但其主宰者君也父也将也。使用者臣也子也卒也。是犹有理则有气。理气合而为心。而理为其主宰。气为其资具也。夫心也性也一理也。性固是理而并气质而言。则程子曰即气。心固是气而指主宰而言。则朱子曰理也。理之兼气性心无异焉。而所主而言不同也。且夫心无体。以性为体。(朱子说)则性乃心体也。指性曰即理。则指心之体而不可曰理耶。今盛论之曰性即理也。而心不可如此说。以其心能知觉故也。足下之意。盖祟于认知觉而为气也。夫知觉固气也。然心体之上。自有所知觉之理。而气因以知觉之。非此理则气焉能自知觉耶。今以知觉专管归气而心能知觉之。故赚指其本体而为气则恐或未然。盖尝言之。心合理气。有指理言者。有指气言者。而以言其主宰则理也。以言其本体则不得不以所主者而言之。不可并指其资具者而为体也。鄙见本自浅陋。无足可道。而历考朱退相传之旨。所尝得者此也。今蒙盛驳。此是大源头去处。而此若不合则更说甚心。鄙人固
其作用之资具也。理其所主之本体也。理譬则君也。气譬则臣也。理譬则父也。气譬则子也。理譬则将也。气譬则卒也。有人于此。并指君臣而曰国之主。并指父子而曰家之长。并指将卒而曰军之帅。足下其许之否乎。有君则有臣。有父则有子。有将则有卒。然但其主宰者君也父也将也。使用者臣也子也卒也。是犹有理则有气。理气合而为心。而理为其主宰。气为其资具也。夫心也性也一理也。性固是理而并气质而言。则程子曰即气。心固是气而指主宰而言。则朱子曰理也。理之兼气性心无异焉。而所主而言不同也。且夫心无体。以性为体。(朱子说)则性乃心体也。指性曰即理。则指心之体而不可曰理耶。今盛论之曰性即理也。而心不可如此说。以其心能知觉故也。足下之意。盖祟于认知觉而为气也。夫知觉固气也。然心体之上。自有所知觉之理。而气因以知觉之。非此理则气焉能自知觉耶。今以知觉专管归气而心能知觉之。故赚指其本体而为气则恐或未然。盖尝言之。心合理气。有指理言者。有指气言者。而以言其主宰则理也。以言其本体则不得不以所主者而言之。不可并指其资具者而为体也。鄙见本自浅陋。无足可道。而历考朱退相传之旨。所尝得者此也。今蒙盛驳。此是大源头去处。而此若不合则更说甚心。鄙人固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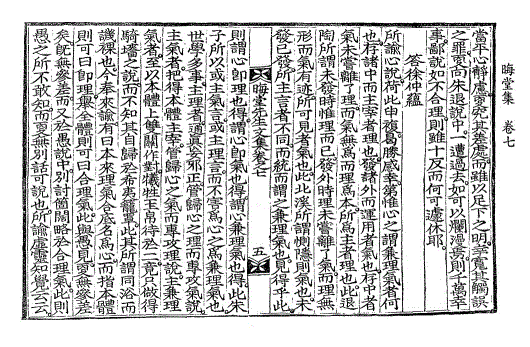 当平心静虑。更究其差处。而虽以足下之明。幸宽其触误之罪。更向朱退说中。一遭过去。如可以烂漫焉。则千万幸事。鄙说如不合理。则虽十反而何可遽休耶。
当平心静虑。更究其差处。而虽以足下之明。幸宽其触误之罪。更向朱退说中。一遭过去。如可以烂漫焉。则千万幸事。鄙说如不合理。则虽十反而何可遽休耶。答徐仲蕴
所谕心说。荷此申复。曷胜感幸。第惟心之谓兼理气者何也。存诸中而主宰者理也。发诸外而运用者气也。存中者气未尝离了理。而气无为而理为本。所为主者理也。此退陶所谓未发时惟理而已。发外时理未尝离了气。而理无形而气有迹。所可见者气也。此北溪所谓恻隐则气也。未发已发。所主言者不同。而统而谓之兼理气也。见得乎此。则谓心即理也得。谓心即气也得。谓心兼理气也得。此朱子所以或主气言。或主理言。而不害为心之为兼理气也。世学多事。主理者。通真妄邪正。管归心之理而专攻气说。主气者。把得本体主宰。管归心之气而专攻理说。主兼理气者。至以本体上双关作对。牺牲玉帛待于二。竟只做得骑墙之说。而不知其自归于希夷笼罩。此其所谓同浴而讥裸也。今奉来谕。有曰本来理气合底名为心。而指本体则可曰即理。举全体则可曰合理气。此与愚见。更无参差矣。既无参差。而又于愚说中。别讨个阔略于合理气。此则愚之所不敢知。而更无别话可说也。所谕虚灵知觉云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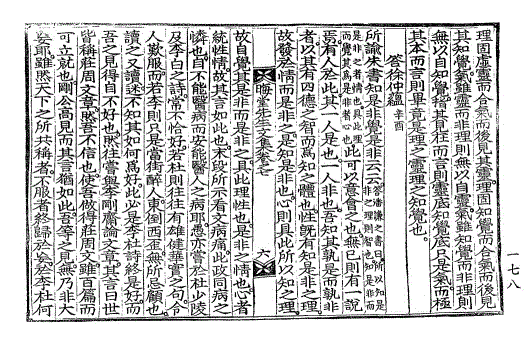 理固虚灵而合气而后见其灵。理固知觉而合气而后见其知觉。气虽灵而非理则无以自灵。气虽知觉而非理则无以自知觉。指其见在而言则灵底知觉底只是气。而极其本而言则毕竟是理之灵理之知觉也。
理固虚灵而合气而后见其灵。理固知觉而合气而后见其知觉。气虽灵而非理则无以自灵。气虽知觉而非理则无以自知觉。指其见在而言则灵底知觉底只是气。而极其本而言则毕竟是理之灵理之知觉也。答徐仲蕴(辛酉)
所谕朱书知是非觉是非云云。(答潘谦之书曰。所以知是非之理则智也。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者心也。)此可以意会之也。无已则有一说焉。有人于此。其一人是也。一人非也。吾知其孰是而孰非者。以其有四德之智而为知之体也。性既有知是非之理。故发于情而是非之。是知是非也。心则具此所以知之理。故自觉其是非而是非之。具此理性也。是非之情也。心者统性情。故其言如此也。末段所示看文病痛。此政同病之怜也。自不能医病而安能医人之病耶。愚亦尝于杜少陵及李白之诗。常不恰好。若杜则往往有雄健华实之句。令人叹服。而若李则只是当街醉人。东倒西歪。无所忌顾也。读之又读。迷不知其如何为好。此必是李杜诗终是好。而吾之见得自不好也。然往尝与李刚斋论文章。其言曰世皆称庄周文章。然吾不信也。使吾做得庄周文。虽百篇而可立就也。刚公高见而其言犹如此。吾等之见。无乃非大妄耶。虽然天下之所共称者。不服者终归于妄。于李杜何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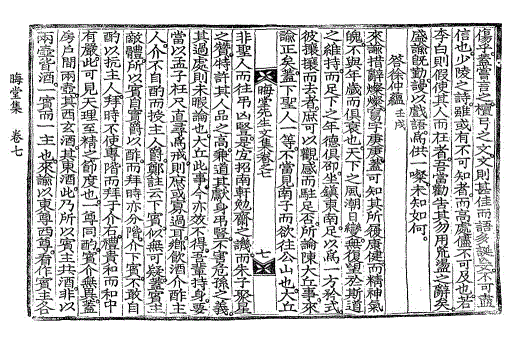 伤乎。盖尝言之。檀弓之文。文则甚佳而语多诞妄。不可尽信也。少陵之诗。虽或有不可知者。而高处尽不可及也。若李白则假使其人而在者。吾当劝告其勿用荒荡之辞矣。盛谕既勤。谩以戏语。为供一哂。未知如何。
伤乎。盖尝言之。檀弓之文。文则甚佳而语多诞妄。不可尽信也。少陵之诗。虽或有不可知者。而高处尽不可及也。若李白则假使其人而在者。吾当劝告其勿用荒荡之辞矣。盛谕既勤。谩以戏语。为供一哂。未知如何。答徐仲蕴(壬戌)
来谕措辞灿灿。写字庚庚。盖可知其所履康健。而精神气魄。不与年岁而俱衰也。天下之风潮日变。无复望于斯道之维持。而足下之年德俱卲。坐镇东南。足以为一方矜式。彼攘攘而去者。庶可以观感而驻足否。所论陈大丘事。来谕正矣。盖下圣人一等。不当见南子而欲往公山也。大丘非圣人而往吊凶竖。是宜招南轩勉斋之讥。而朱子聚星之赞。特许其人品之高。兼道其献身吊竖。不害危孙之义。其过处则未暇论也。大丘此事。今亦效不得。吾辈持身。要当以孟子枉尺直寻为戒。则庶或寡过耳。乡饮酒介酢主人。介不自酌而授主人爵。郑注云下宾。似无可疑。盖宾主敌体。所以宾自实爵以酢。而拜时亦分阶。介下宾。不敢自酌以抗主人。拜时不使专阶而拜于介右。礼贵和而和中有严。此可见天理至精之节度也。一尊同酌。宾介无异。盖房户间两壶。其西玄酒。其东酒。此乃所以宾主共酒。非以两壶皆酒。一宾而一主也。来谕以东尊西尊。看作宾主各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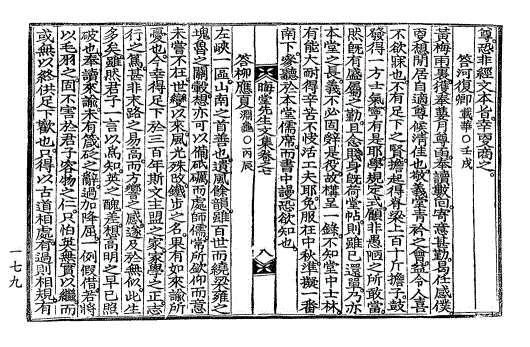 尊。恐非经文本旨。幸更商之。
尊。恐非经文本旨。幸更商之。答河复卿(载华○壬戌)
黄梅雨里。获奉葽月尊函。奉读数回。寄意甚勤。曷任感仆。更想閒居自适尊候清佳也。敬义堂青衿之会。益令人喜不欲寐也。不有足下之贤。担起得脊梁上百十斤担子。鼓发得一方士气。宁有是耶。学规定式。顾非愚陋之所敢当。然既有盛属之勤。且念贱身既荷堂帖。则虽已还单。乃亦本堂之长。义不必固辞是役。故构呈一录。不知堂中士林。有能大耐得辛苦不快活工夫耶。免服在中秋。准拟一番南下。参听于本堂儒席。而书中谩恐欲知也。
答柳应夏(渊龟○丙辰)
左峡一区。山南之首善也。遗风馀韵。虽百世而绕梁雍之块鲁之关毂。想亦可以备砥砺而处师儒。常所钦仰而意未尝不在。世变以来。风光殊改。铁步之名。果有如来谕所忧也。今幸得足下于三百年斯文主盟之家。家学之正。志行之笃。甚非末路之易高。而方响之感。遂及于无似。此生多矣。虽然君子一言以为知。英之丑差。想高明之早已照破也。奉读来谕。未有箴砭之辞。过加降屈。一例假借。若将以毛羽之。固不害于君子容物之仁。只怕英无实以继。而或无以终供足下欢也。只得以古道相处。有过则相规。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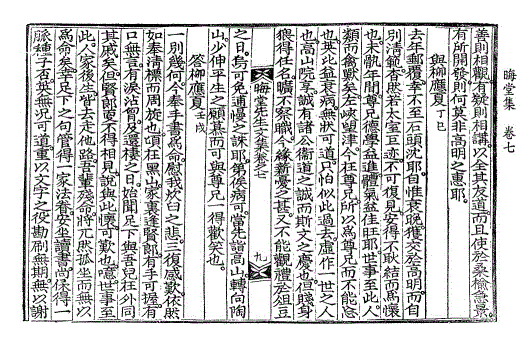 善则相观。有疑则相讲。以全其友道。而且使于桑榆急景。有所开发。则何莫非高明之惠耶。
善则相观。有疑则相讲。以全其友道。而且使于桑榆急景。有所开发。则何莫非高明之惠耶。与柳应夏(丁巳)
去年邮覆。幸不至石头沈耶。自惟衰晚。获交于高明。而自别清范。杳然若太室巨迹。不可复见。安得不耿结而为怀也。未骫年间。尊兄德学益进。体气益佳旺耶。世事至此。人类而禽兽矣。左峡望津。今在尊兄。所以为尊兄而不能忘也。英比益衰病。无状可道。只怕似此过去。虚作一世之人也。高山院享。诚有诸公卫道之诚而斯文之庆也。但贱身猥得任名。旷不察职。今缘薪忧之甚。又不能观礼于俎豆之日。乌可免逋慢之诛耶。第俟病可。当先诣高山。转向陶山。少伸平生之愿慕而可与尊兄一得欢笑也。
答柳应夏(壬戌)
一别几何。今奉手书为命。慰我炊臼之悲。三复感叹。依然如奉清标而周旋也。顷在黑山。家里逢贤郎。有手可握。有口无言。有泪沾胸。及还栖之日。始闻足下与吾儿在外同其戚矣。但贤郎更不得相见。说与此怀。可叹也。噫。世事至此。人家后生。皆去走他路。吾辈残命。将兀然孤坐而无以为命矣。幸足下之句管得一家法眷。安坐读书。尚保得一脉种子否。英无况可道。重以文字之役勘刷无期。无以谢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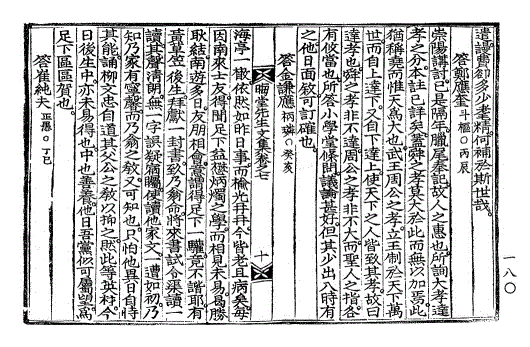 遣。谩费却多少耄精。何补于斯世哉。
遣。谩费却多少耄精。何补于斯世哉。答郑应奎(斗枢○丙辰)
崇阳讲讨。已是隔年。腊尾奉记。故人之惠也。所询大孝达孝之分。本注已详矣。盖舜之孝莫大于此而无以加焉。此犹称尧而惟天为大也。武王周公之孝。立王制于天下万世。而自上达下。又自下达上。使天下之人皆致其孝。故曰达孝也。舜之孝非不达。周公之孝非不大。而圣人之指。各有攸当也。所答小学堂条问。议论甚好。但其少出入时有之。他日面叙。可订确也。
答金谦应(柄璘○癸亥)
海亭一散。依然如昨日事。而榆光冉冉。今皆老且病矣。每因南来士友。得闻足下益懋炳烛之学。而相见未易。曷胜耿结。南游多日。友朋相会。意谓得足下一驩。竟不谐耶。有黄草笠后生。拜献一封书。致乃翁命。将来书试令渠读一读。其声清朗。无一字误疑宿瞩。使读他家文。一遭如初。乃知乃家有宁馨。而乃翁之教。又可知也。只怕他异日自恃其能。诵柳文忠自道其父公之教以抑之。然此等英材。今日后生中。亦未易得也。中也善养。他日吾党似可属望。为足下区区贺也。
答崔纯夫(正愚○丁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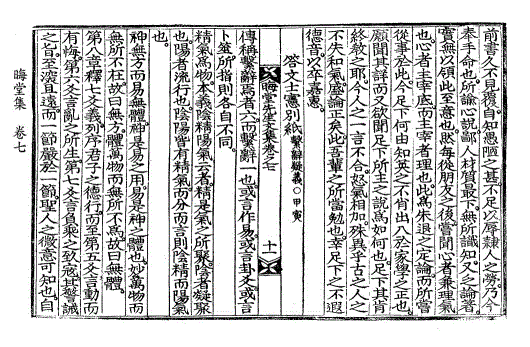 前书久不见覆。自知愚陋之甚。不足以辱隶人之劳。乃今奉手命也。所谕心说。鄙人材质最下。无所识知。又乏论著。实无以领此至意也。然每从朋友之后。尝闻心者兼理气也。心者主宰底。而主宰者理也。此为朱退之定论。而所尝从事于此。今足下何由知英之不肖出入于家学之正也。愿闻其详而又欲闻足下所主之说为如何也。足下其肯终教之耶。今人之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殊异乎古之人之不失和气。盛论正矣。此吾辈之所当勉也。幸足下之不遐德音。以卒嘉惠。
前书久不见覆。自知愚陋之甚。不足以辱隶人之劳。乃今奉手命也。所谕心说。鄙人材质最下。无所识知。又乏论著。实无以领此至意也。然每从朋友之后。尝闻心者兼理气也。心者主宰底。而主宰者理也。此为朱退之定论。而所尝从事于此。今足下何由知英之不肖出入于家学之正也。愿闻其详而又欲闻足下所主之说为如何也。足下其肯终教之耶。今人之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殊异乎古之人之不失和气。盛论正矣。此吾辈之所当勉也。幸足下之不遐德音。以卒嘉惠。答文士宪别纸(系辞疑义○甲寅)
传称系辞焉者六。而系辞一也。或言作易。或言卦爻。或言卜筮。所指则各自不同。
精气为物。本义阴精阳气云者。精是气之所聚。阴者凝聚也。阳者流行也。阴阳皆有精气。而分而言则阴精而阳气也。
神无方而易无体。神是易之用。易是神之体也。妙万物而无所不在。故曰无方。体万物而无所不为。故曰无体。
第八章释七爻义。列序君子之德行。而至第五爻言动而有悔。第六爻言乱之所生。第七爻言负乘之致寇。其警诫之旨。至深且远。而一节严于一节。圣人之微意可知也。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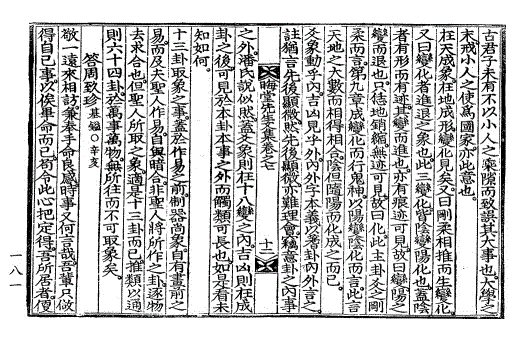 古君子未有不以小人之乘隙而致误其大事也。大学之末。戒小人之使为国家。亦此意也。
古君子未有不以小人之乘隙而致误其大事也。大学之末。戒小人之使为国家。亦此意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此三变化。皆阴变阳化也。盖阴者有形而有迹。其变而进也。亦有痕迹可见。故曰变。阳之变而退也。只恁地销缩。无迹可见。故曰化。此主卦爻之刚柔而言。第九章成变化而行鬼神。以阳变阴化而言。此言天地之大数而相得相合。阴但随阳而化成之而已。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内外字本义以蓍卦内外言之。注犹言先后显微。然先后显微。亦难理会。窃意卦之内事之外。潘氏说似然。盖爻象则在十八变之内。吉凶则在成卦之后。可见于本卦本事之外而触类可长也。如是看未知如何。
十三卦取象之事。盖于作易之前。制器尚象。自有画前之易。而及夫圣人作易。自与暗合。非圣人将所作之卦。逐物去求合也。但圣人所取之象。适是十三卦而已。推类以通则六十四卦。于万事万物。无所往而不可取象矣。
答周致珍(基镒○辛亥)
敬一远来相访。兼奉手命良感。时事又何言哉。吾辈只做得自己事。以俟毕命而已。苟令此心把定得。吾所居者。便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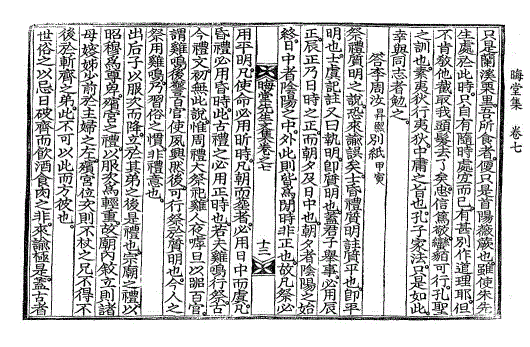 只是兰溪栗里。吾所食者。便只是首阳薇蕨也。虽使朱先生处于此时。只自有随时处宜而已。有甚别作道理耶。但不肯教他截取我头发去了矣。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孔圣之训也。素夷狄行夷狄。中庸之旨也。孔子家法。只是如此。幸与同志者勉之。
只是兰溪栗里。吾所食者。便只是首阳薇蕨也。虽使朱先生处于此时。只自有随时处宜而已。有甚别作道理耶。但不肯教他截取我头发去了矣。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孔圣之训也。素夷狄行夷狄。中庸之旨也。孔子家法。只是如此。幸与同志者勉之。答李周汝(升熙)别纸(甲寅)
祭礼质明之说。恐来谕误矣。士昏礼质明注质平也。即平明也。士虞记注又曰执明。即质明也。盖君子举事。必用辰正。辰正乃日时之正。而朝夕及日中也。朝夕者阴阳之始终。日中者阴阳之中。外此则皆为閒时非正也。故凡祭必用平明。凡使命必用昕时。凡朝而葬者。必用日中而虞。凡昏礼必用昏时。此古礼之必用正时也。若夫鸡鸣行祭。古今礼文。初无此说。惟周礼大祭祀。鸡人夜嘑旦以叫百官。谓鸡鸣后警百官使夙兴然后。可行祭于质明也。今人之祭用鸡鸣。乃习俗之惯。非礼意也。
出后子以服次而降。立于其弟之后是礼也。宗庙之礼。以昭穆为尊卑。殡宫之礼。以服次为轻重。故庙内叙立则诸母嫂姊少前于主妇之左。殡宫位次则不杖之兄不得不后于斩齐之弟。此不可以此而方彼也。
世俗之以忌日破齐而饮酒食肉之非。来谕极是。盖古者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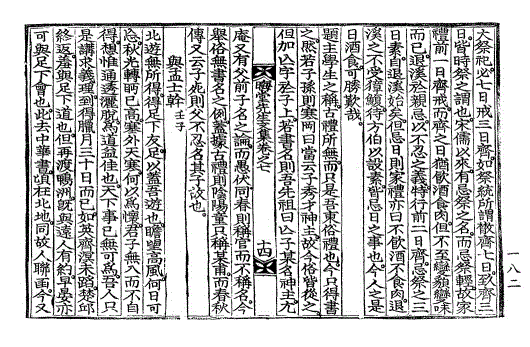 大祭祀。必七日戒三日齐。如祭统所谓散齐七日。致齐三日。皆时祭之谓也。宋儒以来。有忌祭之名。而忌祭轻。故家礼前一日齐戒。而齐之日犹饮酒食肉。但不至变貌变味而已。退溪于亲忌。以不忍之义。特行前二日齐。忌祭之三日素。自退溪始矣。但忌日则家礼亦曰不饮酒不食肉。退溪之不受獐鳆。待方伯以设素。皆忌日之事也。今人之是日酒食。可胜叹哉。
大祭祀。必七日戒三日齐。如祭统所谓散齐七日。致齐三日。皆时祭之谓也。宋儒以来。有忌祭之名。而忌祭轻。故家礼前一日齐戒。而齐之日犹饮酒食肉。但不至变貌变味而已。退溪于亲忌。以不忍之义。特行前二日齐。忌祭之三日素。自退溪始矣。但忌日则家礼亦曰不饮酒不食肉。退溪之不受獐鳆。待方伯以设素。皆忌日之事也。今人之是日酒食。可胜叹哉。题主学生之称。古礼所无。而只是吾东俗礼也。今只得书之。然若子孙则寒冈曰当云子秀才神主。故今俗皆从之。但加亡字于子上。若书名则吾先祖曰亡子某名神主。尤庵又有父前子名之论。而愚伏,同春则称官而不称名。今举俗无书名之例。盖据古礼则阴阳童只称某甫。而春秋传又云子死则父不忍名其子故也。
与孟士干(壬子)
北游无所得。得足下友。足以盖吾游也。瞻望高风。何日可忘。秋光转眄已高。塞外天寒。何以为怀。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想惟通透洒脱。为道益佳也。天下事已无可为。吾人只是讲求义理。到得腊月三十日而已。如英齐溟未蹈。楚邱终返。羞与足下道也。但再渡鸭洲。既与远人有约。早晏亦可与足下会也。此去中华书。顷在北地。同故人联函。今又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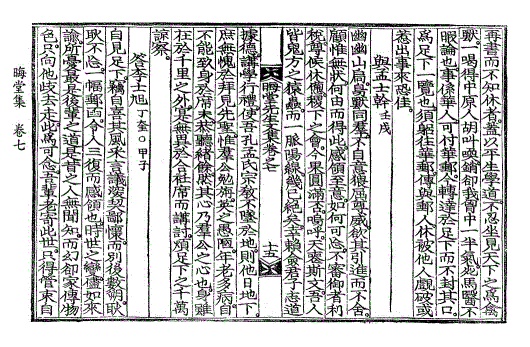 再书而不知休者。盖以平生学道。不忍坐见天下之为禽兽。一喝得中原人胡叫唤。销却我胸中一半气。死马医不暇论也。事系华人。可付华邮。今转达于足下而不封其口。为足下一览也。须躬往华邮。传与邮人。休被他人觑破或惹出事来恐佳。
再书而不知休者。盖以平生学道。不忍坐见天下之为禽兽。一喝得中原人胡叫唤。销却我胸中一半气。死马医不暇论也。事系华人。可付华邮。今转达于足下而不封其口。为足下一览也。须躬往华邮。传与邮人。休被他人觑破或惹出事来恐佳。与孟士干(壬戌)
幽幽山扃。鸟兽同群。不自意猥屈尊威。欲其引进而不舍。顾惟无状。何由而得此。感领至意。如何可忘。不审御者利税。尊候休惫。稷下之会。今果圆满否。呜呼。天丧斯文。吾人皆鬼方之猿虫。而一脉阳线。几已绝矣。幸赖佥君子志道据德。讲学行礼。使吾孔孟氏宗教不坠于地。则他日地下。庶无愧于拜见先圣。惟群公勉旃。英之愚陋。年老多病。自不能致身于席末。恭听绪馀。然其心乃群公之心也。身虽在于千里之外。寔无异于合衽席而讲讨。烦足下之千万谅察。
答李士旭(丁奎○甲子)
自见足下。窃自喜其风采言议深契鄙怀。而别后数朔。耿耿不忘。一幅邮函。令人三复而感领也。时世之变。尽如来谕。所忧最是后辈之道是昔之人无闻知。而幻却家传物色。只向他歧去走。此为可念。吾辈老寄此世。只得管束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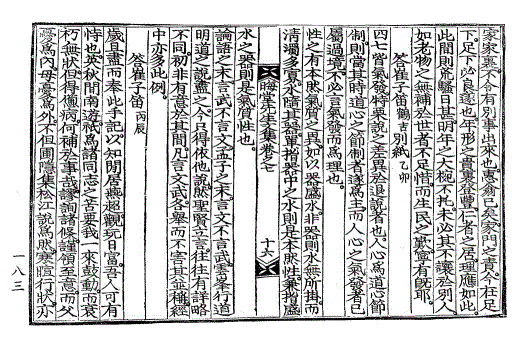 家家里。不令有别事出来也。惠翁已矣。家门之责。今在足下。足下必良遂也。年形之贵里登丰。仁者之居。理应如此。此间则荒骚日甚。明年之大碗不托。未必其不让于别人。如老物之无补于世者不足惜。而生民之叹。宁有既耶。
家家里。不令有别事出来也。惠翁已矣。家门之责。今在足下。足下必良遂也。年形之贵里登丰。仁者之居。理应如此。此间则荒骚日甚。明年之大碗不托。未必其不让于别人。如老物之无补于世者不足惜。而生民之叹。宁有既耶。答崔子笛(鹤吉)别纸(乙卯)
四七皆气发。特栗说之差异于退说者也。人心为道心节制。则当其时道心之节制者遂为主。而人心之气发者已属过境。不必言气发而为理也。
性之有本然气质之异。如以器盛水。非器则水无所挂。而清浊多寡。水随其器。单指器中之水则是本然性。兼指盛水之器则是气质性也。
论语之末。言武不言文。孟子之末。言文不言武。云峰行道明道之说尽之。今只得依他说。然圣贤立言。往往有详略不同。初非有意于其间。凡言文武。各举而不害其并称。经中亦多此例。
答崔子笛(丙辰)
岁且尽而奉此手记。以知閒居燕超。观玩日富。吾人可有恃也。英秋间南游。祇为诸同志之苦要我一来鼓动。而衰朽无状。但得惫病。何补于事哉。谬询诸条。谨领至意。而父忧为内。母忧为外。不但圃隐集松江说为然。寒暄行状。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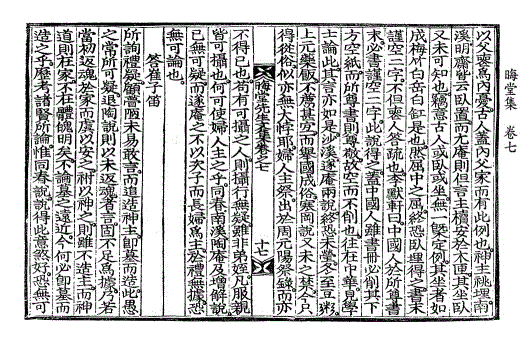 以父丧为内忧。古人盖内父家而有此例也。神主祧埋。南溪,明斋皆云卧置。而尤庵则但言主椟安于木匣。其坐卧又未可知也。窃意古人或卧或坐。无一槩定例。其坐者如成梅竹白岳白缸是也。然屈中之屈。终恐卧埋得之。书末谨空二字。不但丧人答疏也。李默轩曰。中国人于所尊书末。必书谨空二字。此说得之。盖中国人虽书册必削其下方空纸。而所尊书则尊敬。故空而不削也。往在中华。见学士论此。其言亦如是。沙溪,遂庵两说。终恐未莹。冬至豆粥。上元药饭。不荐甚宜。而举国成俗。寒冈说又未之禁。今只得从俗。似亦无大悖耶。妇人主祭。出于周元阳祭录。而亦不得已也。苟有可摄之人。则摄行无疑。虽非弟侄。凡服亲皆可摄也。何可使妇人主之乎。同春,南溪,陶庵及增解说。已无可疑。而遂庵之不以次子而长妇为主。于礼无据。恐无可论也。
以父丧为内忧。古人盖内父家而有此例也。神主祧埋。南溪,明斋皆云卧置。而尤庵则但言主椟安于木匣。其坐卧又未可知也。窃意古人或卧或坐。无一槩定例。其坐者如成梅竹白岳白缸是也。然屈中之屈。终恐卧埋得之。书末谨空二字。不但丧人答疏也。李默轩曰。中国人于所尊书末。必书谨空二字。此说得之。盖中国人虽书册必削其下方空纸。而所尊书则尊敬。故空而不削也。往在中华。见学士论此。其言亦如是。沙溪,遂庵两说。终恐未莹。冬至豆粥。上元药饭。不荐甚宜。而举国成俗。寒冈说又未之禁。今只得从俗。似亦无大悖耶。妇人主祭。出于周元阳祭录。而亦不得已也。苟有可摄之人。则摄行无疑。虽非弟侄。凡服亲皆可摄也。何可使妇人主之乎。同春,南溪,陶庵及增解说。已无可疑。而遂庵之不以次子而长妇为主。于礼无据。恐无可论也。答崔子笛
所询礼疑。顾瞢陋未易敢言。而追造神主。即墓而造。此愚之常所可疑。退陶说则以未返魂者言。固不足为据。乃若当初返魂于家而虞以安之。祔以神之。则虽不造主。而神道则在家。不在体魄明矣。不论墓之远近。今何必即墓而造之乎。历考诸贤所论。惟同春说。说得此意煞好。恐无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4L 页
 疑。今令孙将入后。则必将卜日行告庙之礼。因此时告庙毕。(若已行入后之礼。则节荐及本位忌祭时亦可。)净扫室堂。设父祖灵座两虚位于堂上。仿古人剪纸招魂之礼。(陶庵说)以小竹竿挂一幅纸。书显祖考某官府君招魂之位。一书显考云云。各倚于灵座之傍。主人进灵座前跪。祝跪告曰孝孙某。今以有事于显祖考某官府君。敢请尊灵降居神位。考位亦告之如初。令善书者先题祖主。次题考主。(节次依家礼。)题毕。祝奉主置灵座。设酒果脯醢。主人焚香降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跪献爵。祝跪读祝。先告祖位。后告考位。祝式当曰年月干支云云。丧葬之日。遭值变乱。未及造主。不肖今入承宗祀。式遵礼意。追造神主。伏惟尊灵。是凭是依。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读毕怀之。主人以下皆再拜。祝奉主置别室净处。厥明日质明。设位于正厅。主人告于本庙曰孝玄孙某。今以合享。有事于显祖考显考。敢请显高祖考妣显曾祖考妣神主出就厅事。遂奉主出。又就别室。告于父祖神主曰敢请神主出就厅事。自高祖以下同堂并设。遂行祫祭。三献行事。祝板自高祖以下。列书曰小孙某入承宗祀。追造显祖考显考神主。式遵典礼。隮入于庙。合荐精禋。不胜永慕。谨以清酌庶羞云云。祭毕隮配于庙。如何如何。新建祠宇。移奉神主。祝出主时。当告曰新建祠堂于正寝之南。请奉
疑。今令孙将入后。则必将卜日行告庙之礼。因此时告庙毕。(若已行入后之礼。则节荐及本位忌祭时亦可。)净扫室堂。设父祖灵座两虚位于堂上。仿古人剪纸招魂之礼。(陶庵说)以小竹竿挂一幅纸。书显祖考某官府君招魂之位。一书显考云云。各倚于灵座之傍。主人进灵座前跪。祝跪告曰孝孙某。今以有事于显祖考某官府君。敢请尊灵降居神位。考位亦告之如初。令善书者先题祖主。次题考主。(节次依家礼。)题毕。祝奉主置灵座。设酒果脯醢。主人焚香降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跪献爵。祝跪读祝。先告祖位。后告考位。祝式当曰年月干支云云。丧葬之日。遭值变乱。未及造主。不肖今入承宗祀。式遵礼意。追造神主。伏惟尊灵。是凭是依。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读毕怀之。主人以下皆再拜。祝奉主置别室净处。厥明日质明。设位于正厅。主人告于本庙曰孝玄孙某。今以合享。有事于显祖考显考。敢请显高祖考妣显曾祖考妣神主出就厅事。遂奉主出。又就别室。告于父祖神主曰敢请神主出就厅事。自高祖以下同堂并设。遂行祫祭。三献行事。祝板自高祖以下。列书曰小孙某入承宗祀。追造显祖考显考神主。式遵典礼。隮入于庙。合荐精禋。不胜永慕。谨以清酌庶羞云云。祭毕隮配于庙。如何如何。新建祠宇。移奉神主。祝出主时。当告曰新建祠堂于正寝之南。请奉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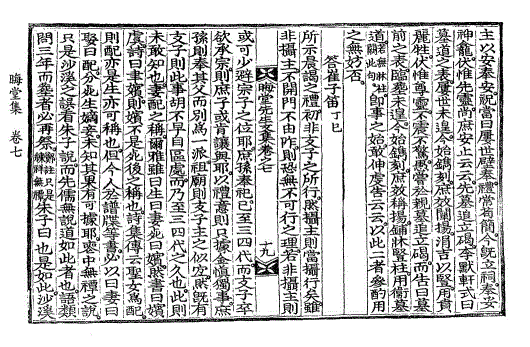 主以安奉安。祝当曰屡世壁奉。礼常苟简。今既立祠。奉妥神龛。伏惟先灵。尚庶安止云云。先墓追立碣。李默轩式曰墓道之表。屡世未遑。今始镌刻。庶效阐扬。涓吉以竖。用贲丽牲。伏惟尊灵。不震不惊。愚尝于亲墓追立碣。而告曰墓前之表。临葬未遑。今始镌刻。庶效称扬。铺床竖柱。用卫墓道。(若无床柱。阙此句。)即事之始。敢伸虔告云云。以此二者参酌用之无妨否。
主以安奉安。祝当曰屡世壁奉。礼常苟简。今既立祠。奉妥神龛。伏惟先灵。尚庶安止云云。先墓追立碣。李默轩式曰墓道之表。屡世未遑。今始镌刻。庶效阐扬。涓吉以竖。用贲丽牲。伏惟尊灵。不震不惊。愚尝于亲墓追立碣。而告曰墓前之表。临葬未遑。今始镌刻。庶效称扬。铺床竖柱。用卫墓道。(若无床柱。阙此句。)即事之始。敢伸虔告云云。以此二者参酌用之无妨否。答崔子笛(丁巳)
所示晨谒之礼。初非支子之所行。然摄主则当摄行矣。虽非摄主。不开门不由阼。则恐无不可行之理。若非摄主则或可少避宗子之位耶。庶孙奉祀。已至三四代。而支子卒欲承宗。则庶子或肯让与耶。以礼意则只据金慎独事。庶孙则奉其父而别为一派。祖庙则支子主之似宜。然既有支子则此事胡不早自区处。而乃至三四代之久也。此则未敢知也。妻配之称。尔雅虽曰生曰妻死曰嫔。然书曰嫔虞。诗曰聿嫔。则嫔不是死后之称也。诗集传云圣女为配。则配亦是生亦可称也。但今人于谱牒等书。必以曰妻曰娶曰配。分死生嫡妾。未知其果有可据耶。丧中无禫之说。只是沙溪之误看朱子说。而先儒无说道如此者也。语类问三年而葬者必再祭。(郑注只是练祥无禫。)朱子曰也是如此。沙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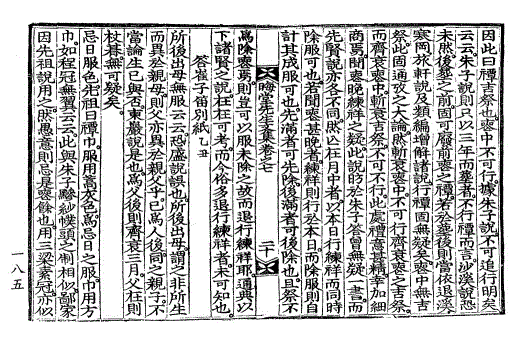 因此曰禫吉祭也。丧中不可行。据朱子说。不可追行明矣云云。朱子说则只以三年而葬者。不行禫而言。沙溪说恐未然。后葬之前。固可废前丧之禫。若于葬后则当依退溪,寒冈,旅轩说及类编增解诸说。行禫固无疑矣。丧中无吉祭。此固通考之大论。然斩衰丧中。不可行齐衰丧之吉祭。而齐衰丧中。斩衰吉祭。不可不行。此处礼意甚精。幸加细商焉。闻丧晚练祥之疑。此说昉于朱子答曾无疑一书。而先贤说亦各不同。然亡在月中者。以本日行练祥而同时除服可也。若闻丧甚晚者。练祥则行于本日。而除服则自计其成服可也。先满者可先除。后满者可后除也。且祭不为除丧焉。则岂可以服未除之故而退行练祥耶。通典以下诸贤之说。在在可考。而今俗多退行练祥者。未可知也。
因此曰禫吉祭也。丧中不可行。据朱子说。不可追行明矣云云。朱子说则只以三年而葬者。不行禫而言。沙溪说恐未然。后葬之前。固可废前丧之禫。若于葬后则当依退溪,寒冈,旅轩说及类编增解诸说。行禫固无疑矣。丧中无吉祭。此固通考之大论。然斩衰丧中。不可行齐衰丧之吉祭。而齐衰丧中。斩衰吉祭。不可不行。此处礼意甚精。幸加细商焉。闻丧晚练祥之疑。此说昉于朱子答曾无疑一书。而先贤说亦各不同。然亡在月中者。以本日行练祥而同时除服可也。若闻丧甚晚者。练祥则行于本日。而除服则自计其成服可也。先满者可先除。后满者可后除也。且祭不为除丧焉。则岂可以服未除之故而退行练祥耶。通典以下诸贤之说。在在可考。而今俗多退行练祥者。未可知也。答崔子笛别纸(乙丑)
所后出母无服云云。恐盛说误也。所后出母。谓之非所生而异于亲母。则父亦异于亲父乎。己为人后。同之亲子。不当论生己与否。东岩说是也。为父后则齐衰三月。父在则杖期。无可疑矣。
忌日服色。先祖曰禫巾。服用蒿灰色。为忌日之服。巾用方巾。如程冠无翼云云。此与朱子黪纱幞头之制相似。鄙家因先祖说用之。然愚意则忌是丧馀也。用三梁素冠。亦似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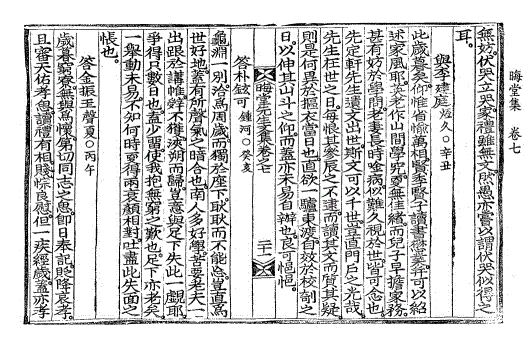 无妨。伏哭立哭。家礼虽无文。然愚亦尝以谓伏哭似得之耳。
无妨。伏哭立哭。家礼虽无文。然愚亦尝以谓伏哭似得之耳。与李建庭(烜久○辛丑)
此岁暮矣。仰惟省愉万相。贤季贤子读书懋业。并可以绍述家风耶。英老作山间学究。更无佳绪。而儿子早担家务。甚有妨于学问。老妻长时唫病。似难久视于世。皆可念也。先定轩先生遗文出世。斯文可以千世。岂直门户之光哉。先生在世之日。每恨其参辰之不逮。而读其文而质其疑。则是何异于抠衣当日也。直欲一驴东渡。自效于校剞之日。以伸其山斗之仰。而盖亦未易自办也。良可悒悒。
答朴铉可(钟河○癸亥)
龟渊一别。洽为周岁。而独于座下。耿耿而不能忘。岂直为世好地。盖有所声气之暗合也。南人多好学。苦要老夫一出跟于讲帷。辞不获。浃朔而归。岂意与足下失此一觑耶。争得只数日也。盍少留。使我抱无穷之叹也。足下亦老矣。一举动未易。不知何时更得两衰颜相对。吐尽此失面之怅也。
答金振玉(声夏○丙午)
岁暮穷寮。无与为怀。第切同志之思。即日奉记。贬降哀孝。且审天佑孝思。读礼有相。贱悰良慰。但一疾经岁。盖亦孝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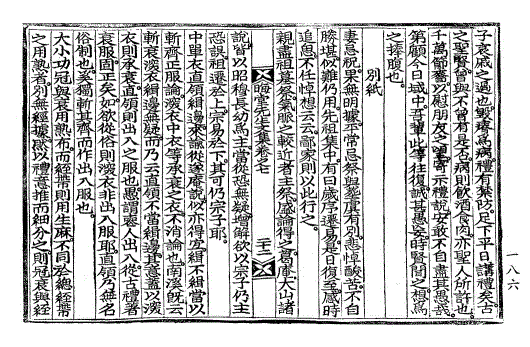 子哀戚之过也。毁瘠为病。礼有禁防。足下平日讲礼矣。古之圣贤。曾与不曾有是否。病则饮酒食肉。亦圣人所许也。千万节啬。以慰朋友之望。寄示礼说。安敢不自尽其愚哉。第顾今日域中。吾辈此等往复。诚甚愚妄。时贤闻之。想为之捧腹也。
子哀戚之过也。毁瘠为病。礼有禁防。足下平日讲礼矣。古之圣贤。曾与不曾有是否。病则饮酒食肉。亦圣人所许也。千万节啬。以慰朋友之望。寄示礼说。安敢不自尽其愚哉。第顾今日域中。吾辈此等往复。诚甚愚妄。时贤闻之。想为之捧腹也。别纸
妻忌祝。果无明据。平常忌祭与葬虞有别。悲悼酸苦。不自胜堪。似难仍用。先祖集中。有曰岁序迁易。是日复至。感时追思。不任悼想云云。鄙家则以此行之。
亲尽祖墓祭。气脉之较近者主祭。盛论得之。葛庵,大山诸说。皆以昭穆长幼为主。当从恐无疑。增解欲以宗子仍主恐误。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其可仍宗子耶。
中单衣直领缉边。来谕从遂庵说。似亦得宜。缉不缉当以斩齐正服论。深衣中衣等承衰之衣。不消论也。南溪既云斩衰深衣缉边无疑。而乃云直领不当缉边。其意盖以深衣则承衰。直领则出入之服也。愚谓丧人出入。从古礼著衰服。固正矣。如欲从俗则深衣非出入服耶。直领乃无名俗制也。奚独斩其齐而作出入服也。
大小功冠与衰用熟布。而绖带则用生麻。不同于缌绖带之用熟者。别无经据。然以礼意推而细分之。则冠衰与绖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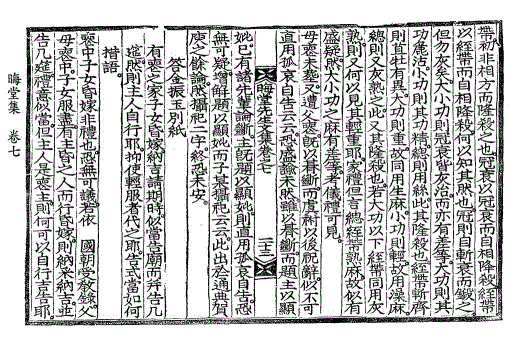 带。初非相方而隆杀之也。冠衰以冠衰而自相降杀。绖带以绖带而自相降杀。何以知其然也。冠则自斩衰而锻之。但勿灰矣。大小功则冠衰皆灰治。而亦有差等。大功则其功粗沽。小功则其功精。缌则用丝。此其隆杀也。绖带斩齐则苴牡有异。大功则重。故同用生麻。小功则轻。故用澡麻。缌则又灰熟之。此又其隆杀也。若大功以下绖带同用灰熟。则又何以见其轻重耶。家礼但言缌绖带熟麻。故似有盛疑。然大小功之麻有差等。考仪礼可见。
带。初非相方而隆杀之也。冠衰以冠衰而自相降杀。绖带以绖带而自相降杀。何以知其然也。冠则自斩衰而锻之。但勿灰矣。大小功则冠衰皆灰治。而亦有差等。大功则其功粗沽。小功则其功精。缌则用丝。此其隆杀也。绖带斩齐则苴牡有异。大功则重。故同用生麻。小功则轻。故用澡麻。缌则又灰熟之。此又其隆杀也。若大功以下绖带同用灰熟。则又何以见其轻重耶。家礼但言缌绖带熟麻。故似有盛疑。然大小功之麻有差等。考仪礼可见。母丧未葬。又遭父丧。既以期断。而虞祔以后祝辞。似不可直用孤哀自告云云。恐盛谕未然。虽以期断。而题主以显妣。已有诸先辈论断。主既题以显妣。则直用孤哀自告。恐无可疑。增解题以显妣而子某摄祀云云。此出于通典贺庾之馀论。然摄祀二字。终恐未安。
答金振玉别纸
有丧之家子女昏嫁。纳吉请期时。似当告庙而并告几筵。然则主人自行耶。抑使轻服者代之耶。告式当如何措语。
丧中子女昏嫁非礼也。恐无可议。若依 国朝受教录。父母丧中。子女服尽。有主昏之人而行昏嫁。则纳采纳吉。并告几筵。礼意似当。但主人是丧主。则何可以自行吉告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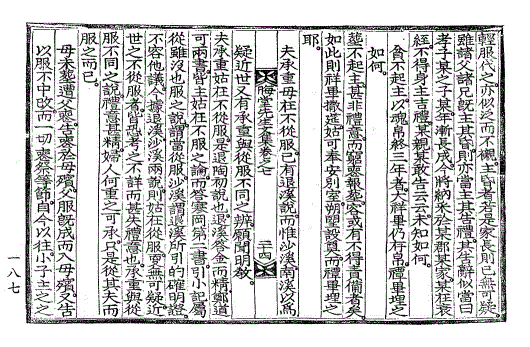 轻服代之。亦似泛而不衬。主昏者若是家长则已无可疑。虽诸父诸兄既主其昏。则亦当主其告礼。其告辞似当曰孝子某之子某。年渐长成。今将纳采于某郡某家。某在衰绖。不得身主吉礼。某亲某敢告云云。未知如何。
轻服代之。亦似泛而不衬。主昏者若是家长则已无可疑。虽诸父诸兄既主其昏。则亦当主其告礼。其告辞似当曰孝子某之子某。年渐长成。今将纳采于某郡某家。某在衰绖。不得身主吉礼。某亲某敢告云云。未知如何。贫不起主。以魂帛终三年者。大祥毕仍存帛。禫毕埋之如何。
葬不起主。甚非礼意。而穷丧报葬。容或有不得责备者矣。如此则祥毕撤筵。姑可奉安别室。朔望设奠。而禫毕埋之耶。
夫承重母在不从服。已有退溪说。而惟沙溪,南溪以为疑近世又有承重与从服不同之辨。愿闻明教。
夫承重姑在不从服。是退陶初说也。退溪答金而精,郑道可两书。皆主姑在不服之论。而答寒冈第二书。引小记属从虽没也服之说。谓当从服。沙溪谓退溪所引的确明證。不容他议。今据退溪,沙溪两说。则姑在从服。更无可疑。近世之不从服者。皆恐考之不详而甚失礼意也。承重与从服不同之说。礼意甚精。妇人何重之可承。只是从其夫而服之而已。
母未葬遭父丧。告丧于母殡。父服既成而入母殡。又告以服不中改。而一切丧祭等节。自今以往。小子主之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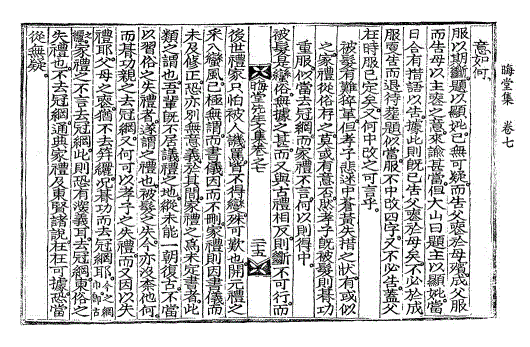 意如何。
意如何。服以期断。题以显妣。已无可疑。而告父丧于母殡。成父服而告母以主丧之意。来谕甚当。但大山曰题主以显妣。当日合有措语以告。据此则既已告父丧于母矣。不必于成服更告而退待葬题似当。服不中改四字。又不必告。盖父在时服已定矣。又何中改之可言乎。
被发有难猝革。但孝子悲迷中苍黄失措之状。有或似之。家礼从俗存之。莫或有意否。然孝子既被发则期功重服。似当去冠网。而家礼不言。何以则得中。
被发是蛮俗。无据之甚。而又与古礼相反。则断不可行。而后世礼家只怕被人讥骂。皆不得变。殊可叹也。开元礼之采入蛮风。已极无谓。而书仪因而不删。家礼则因书仪而未及修正。恐亦别无意义于其间。家礼之为未定书者。此类之谓也。吾辈既不居议礼之地。纵未能一朝复古。不当以习俗之失礼者。遂谓之礼也。被发之失。今亦没柰他何。而期功亲之去冠网。又何可以孝子之失礼。而又因以失礼耶。父母之丧。犹不去笄纚。况期功而去冠网耶。(今之网巾。即古之纚。)家礼之不言去冠网。此则恐有深义耳。去冠网。东俗之失礼也。不去冠网。通典家礼及东贤诸说。在在可据。恐当从无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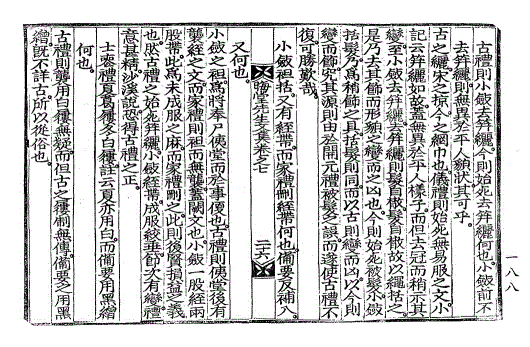 古礼则小敛去笄纚。今则始死去笄纚何也。小敛前不去笄纚。则无异于平人貌状。其可乎。
古礼则小敛去笄纚。今则始死去笄纚何也。小敛前不去笄纚。则无异于平人貌状。其可乎。古之纚。宋之掠。今之网巾也。仪礼则始死无易服之文。小记云笄纚如故。盖无异于平人样子。而但去冠而稍示其变。至小敛去笄纚。去笄纚则发自散。发自散故以绳括之。是乃去其饰而形貌之变而之凶也。今则始死被发。小敛括发。乃为稍饰之具。括发则同。而以古则变而凶。以今则变而饰。究其源则由于开元礼被发之误。而遂使古礼不复。可胜叹哉。
小敛袒括。又有绖带。而家礼删绖带何也。备要反补入。又何也。
小敛之袒。为将奉尸侇堂而于事便也。古礼则侇堂后有袭绖之文。而家礼则袒而无袭。盖阙文也。小敛一股绖两股带。此为未成服之麻。而家礼删之。此则后贤损益之义也。然古礼之始死笄纚。小敛绖带。成服绞垂。节次有变。礼意甚精。沙溪说。恐得古礼之正。
士丧礼夏葛屦冬白屦。注云夏亦用白。而备要用黑缯何也。
古礼则袭用白屦无疑。而但古之屦制无传。备要之用黑缯。既不详古。所以从俗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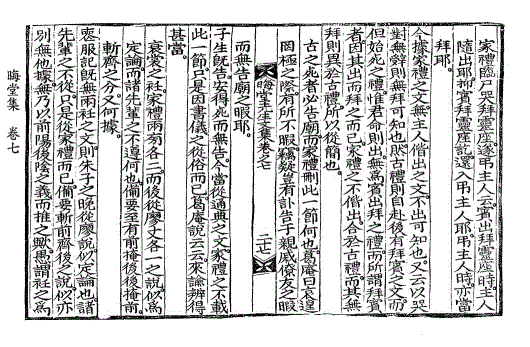 家礼临尸哭拜灵座。遂吊主人云。宾出拜灵座时。主人随出耶。抑宾拜灵座讫。还入吊主人耶。吊主人时。亦当拜耶。
家礼临尸哭拜灵座。遂吊主人云。宾出拜灵座时。主人随出耶。抑宾拜灵座讫。还入吊主人耶。吊主人时。亦当拜耶。今据家礼之文。无主人偕出之文。不出可知也。又云以哭对无辞则无拜可知也。然古礼则自赴后有拜宾之文。而但始死之礼。惟君命则出。无为宾出拜之礼。而所谓拜宾者。因其出而拜之而已。家礼之不偕出。合于古礼。而其无拜则异于古礼。所以从简也。
古之死者必告庙。而家礼删此一节何也。葛庵曰哀遑罔极之际。有所不暇。窃疑岂有讣告于亲戚僚友之暇而无告庙之暇耶。
子生既告。安得死而无告。今当从通典之文。家礼之不载此一节。只是因书仪之从俗而已。葛庵说云云。来谕辨得甚当。
衰裳之衽。家礼两旁各二。而后从廖丈各一之说。似为定论。而诸先辈之不遵何也。备要至有前掩后后掩前。斩齐之分。又何据。
丧服记既无两衽之文。则朱子之晚从廖说。似定论也。诸先辈之不从。只是从家礼而已。备要斩前齐后之说。似亦别无他据。无乃以前阳后阴之义而推之欤。愚谓衽之为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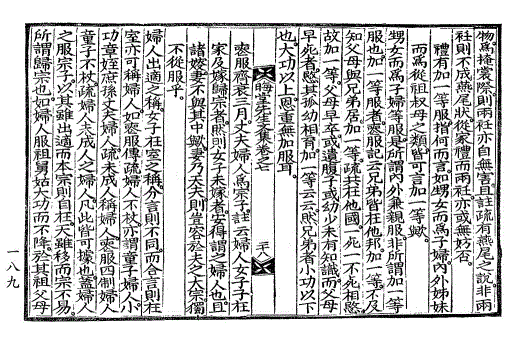 物。为掩裳际。则两衽亦自无害。且注疏有燕尾之说。非两衽则不成燕尾状。从家礼而两衽。亦或无妨否。
物。为掩裳际。则两衽亦自无害。且注疏有燕尾之说。非两衽则不成燕尾状。从家礼而两衽。亦或无妨否。礼有加一等服。指何而言。如甥女而为子妇。内外姊妹而为从祖叔母之类。皆可言加一等欤。
甥女而为子妇等服。是所谓内外兼亲服。非所谓加一等服也。加一等服者。丧服记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与兄弟居。加一等。疏共在他国。一死一不死相悯。故加一等。父母早卒。或遗腹子或幼少未有知识。而父母早死者。悯其孤幼相育。加一等云云。然兄弟者小功以下也。大功以上。恩重无加服耳。
丧服齐衰三月。丈夫妇人为宗子。注云妇人女子子在家及嫁归宗者。然则女子未嫁者。安得谓之妇人也。且诸嫂。妻不与其中欤。妻乃天夫。则岂容于夫之大宗。独不从服乎。
妇人出适之称。女子在室之称。分言则不同。而合言则在室亦可称妇人。如丧服传疏妇人不杖。亦谓童子妇人。小功章侄庶孙丈夫妇人。疏未成人称妇人。丧服四制妇人童子不杖。疏妇人未成人之妇人。凡此皆可据也。盖妇人之服宗子。以其虽出适而本宗则自在。天虽移而宗不易。所谓归宗也。如妇人服祖舅姑大功而不降。于其祖父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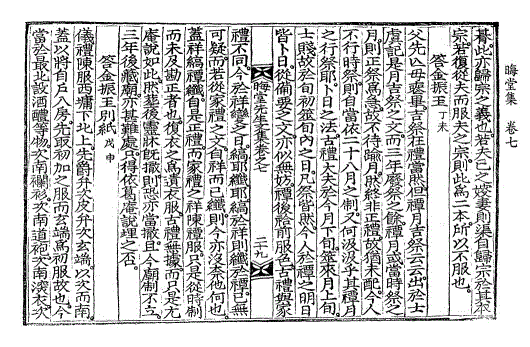 期。此亦归宗之义也。若夫己之嫂妻则渠自归宗于其本宗。若复从夫而服夫之宗。则此为二本。所以不服也。
期。此亦归宗之义也。若夫己之嫂妻则渠自归宗于其本宗。若复从夫而服夫之宗。则此为二本。所以不服也。答金振玉(丁未)
父先亡母丧毕。吉祭在礼当然。但禫月吉祭云云。出于士虞记是月吉祭之文。而三年废祭之馀。禫月或当时祭之月。则正祭为急。故不待踰月。然终非正礼。故犹未配。今人不行时祭。则自当依二十八月之制。又何汲汲乎其禫月之行祭耶。卜日之法。古礼大夫于今月下旬。筮来月上旬。士贱故于旬初筮旬内之日。凡祭皆然。今人于禫之明日皆卜日。从备要之文。亦似无妨。禫后祫前服色。古礼与家礼不同。今于祥变之日。缟耶纤耶。缟于祥则纤于禫。已无可疑。而若从家礼之文。自祥而已纤。则今亦没柰他何也。盖祥缟禫纤。自是正礼。而家礼之祥陈禫服。只是从时制而未及勘正者也。复衣之为遗衣服。古礼无据。而只是尤庵说如此。然葬后灵床既撤。则恐亦当撤。且今庙制不立。三年后藏庙。亦甚难处。只得依葛庵说埋之否。
答金振玉别纸 冠礼疑问(저본에는 없다. 저본의 원목차에 근거하여 보충하였다.)○戊申
仪礼陈服西墉下北上。先爵弁次皮弁次玄端。以次而南。盖以将自户入房。先取初加之服而玄端为初服故也。今当于最北设酒醴等物。次南襕衫。次南道袍。次南深衣。次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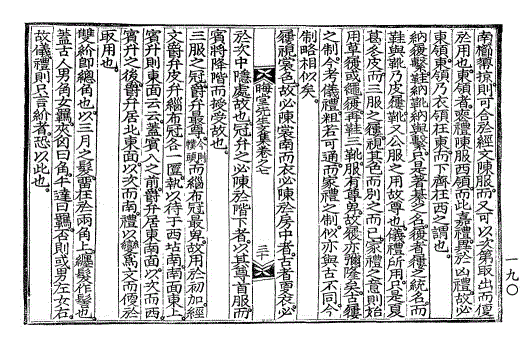 南栉𢄼掠。则可合于经文陈服。而又可以次第取出而便于用也。东领者。丧礼陈服西领。而此嘉礼。异于凶礼。故必东领。东领乃衣领在东。而下齐在西之谓也。
南栉𢄼掠。则可合于经文陈服。而又可以次第取出而便于用也。东领者。丧礼陈服西领。而此嘉礼。异于凶礼。故必东领。东领乃衣领在东。而下齐在西之谓也。纳履系。鞋纳靴纳与系。只是著綦之名。履者屦之统名。而鞋与靴乃皮屦。靴又公服之用故尊也。仪礼所用。只是夏葛冬皮。而三服之屦。视其色而别之而已。家礼之意则始用草履或绳履。再鞋三靴。服有尊卑。故履亦弥隆矣。古屦之制。今考仪礼。粗若可通。而家礼之制。似亦与古不同。今制略相似矣。
屦视裳色。故必陈裳南而衣必陈于房中者。古者更衣。必于次中隐处故也。冠弁之必陈于阶下者。以其尊首服。而宾将降阶而授受故也。
三服之冠。爵弁最尊。(今则幞头。)而缁布冠最卑。故用于初加。经文爵弁皮弁缁布冠各一匴。执以待于西坫南。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云云。盖宾入之前。爵弁居东南面。以次而西。宾升之后。爵弁居北东面。以次而南。礼以变为文而便于取用也。
双紒即总角也。以三月之发。留在于两角上。缠发作髻也。盖古人男角女羁。夹囟曰角。午达曰羁。否则或男左女右。故仪礼则只言紒者。恐以此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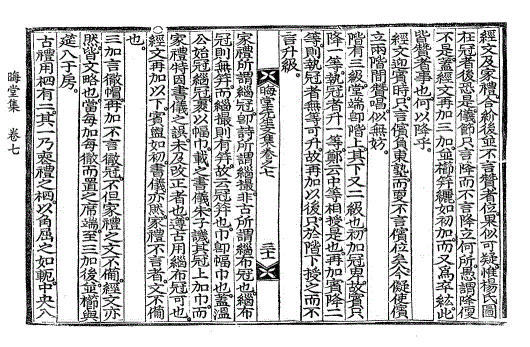 经文及家礼。合紒后并不言赞者位。果似可疑。惟杨氏图在冠者后恐是。仪节只言降而不言降立何所。愚谓降便不是。盖经文再加三加。并栉笄纚如初加。而又为卒纮。此皆赞者事也。何以降乎。
经文及家礼。合紒后并不言赞者位。果似可疑。惟杨氏图在冠者后恐是。仪节只言降而不言降立何所。愚谓降便不是。盖经文再加三加。并栉笄纚如初加。而又为卒纮。此皆赞者事也。何以降乎。经文迎宾时。只言傧负东塾。而更不言傧位矣。今儗使傧立两阶间赞唱。似无妨。
阶有三级。堂端即阶上。其下又二级也。初加冠卑。故宾只降一等。执冠者升一等。郑云中等相授是也。再加宾降二等。则执冠者无等可升。故再加以后。只于阶下授之而不言升级。
家礼所谓缁冠。即诗所谓缁撮。非古所谓缁布冠也。缁布冠则无笄。而缁撮则有笄。故云冠笄也。巾即幅巾也。盖温公始冠缁冠。裹以幅巾。载之书仪。朱子讥其冠上加巾。而家礼特因书仪之误。未及改正者也。遵古用缁布冠可也。
经文再加以下。宾盥如初。书仪亦然。家礼不言者。文不备也。
三加言彻帽。再加不言彻冠。不但家礼之文不备。经文亦然。皆文略也。当每加每彻而置之席端。至三加后。并栉与筵入于房。
古礼用柶有二。其一乃丧礼之柶。以角屈之如轭。中央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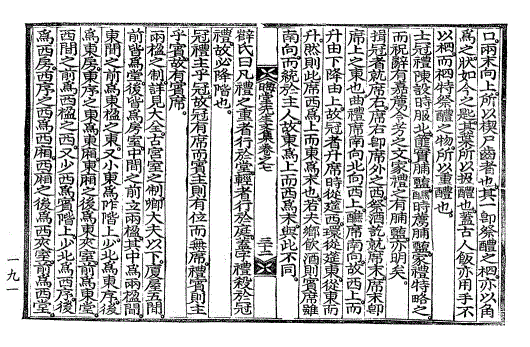 口。两末向上。所以楔尸齿者也。其一即祭醴之柶。亦以角为之。状如今之匙。其叶所以扱醴也。盖古人饭亦用手不以柶。而柶特祭醴之物。所以重醴也。
口。两末向上。所以楔尸齿者也。其一即祭醴之柶。亦以角为之。状如今之匙。其叶所以扱醴也。盖古人饭亦用手不以柶。而柶特祭醴之物。所以重醴也。士冠礼陈设时服北。篚实脯醢。醮时荐脯醢。家礼特略之。而祝辞有嘉荐令芳之文。家礼之有脯醢。亦明矣。
揖冠者就席右。席右即席外之西。祭酒讫就席末。席末即席上之东也。曲礼席南向北向西上。醮席南向。故西上。而升由下降由上。故冠者升席时从筵西。环从筵东。从东而升。然则此席西为上而东为末也。若夫乡饮酒则宾席虽南向。而统于主人。故东为上而西为末。与此不同。
辥氏曰凡礼之重者行于堂。轻者行于庭。盖字礼杀于冠礼。故必降阶也。
冠礼主乎冠。故冠有席而宾主则有位而无席。礼宾则主乎宾。故有宾席。
两楹之制。详见大全。古宫室之制。卿大夫以下。厦屋五间。前皆为堂。后皆为房室。中间之前立两楹。其中为两楹间。东间之前为东楹之东。又小东为阼阶上。少北为东序。后为东房。东序之东为东厢。东厢之后为东夹室。前为东堂。西间之前为西楹之西。又少西为宾阶上。少北为西序。后为西房。西序之西为西厢。西厢之后为西夹室。前为西堂。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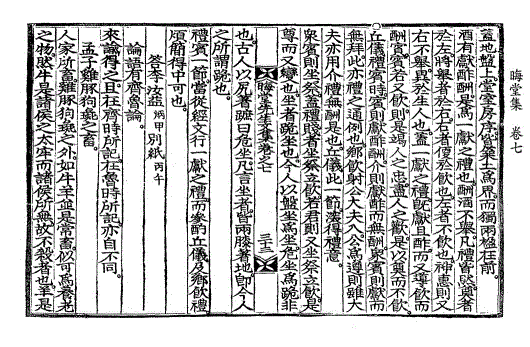 盖地盘上。堂室房序。皆筑土为界。而独两楹在前。
盖地盘上。堂室房序。皆筑土为界。而独两楹在前。酒有献酢酬。是为一献之礼也。酬酒不举。凡礼皆然。奠者于左。将举者于右。右者便于饮也。左者不饮也。神惠则又右不举。异于生人也。盖一献之礼。既献且酢。而又导饮而酬宾。宾若又饮。则是竭人之忠。尽人之欢。是以奠而不饮。
丘仪礼宾时。宾则献酢酬。介则献酢而无酬。众宾则献而无拜。此亦礼之通例也。乡饮射公大夫入。公为遵则虽大夫亦用介礼无酬是也。丘仪此一节。深得礼意。
众宾则坐祭。盖礼贱者坐祭立饮。若君则又坐祭立饮。是尊而又变也。坐者跪坐也。今人以盘坐为坐。危坐为跪非也。古人以尻著蹠曰危坐。凡言坐者。皆两膝著地。即今人之所谓跪也。
礼宾一节。当从经文行一献之礼。而参酌丘仪及乡饮礼。烦简得中可也。
答李汝益(炳甲)别纸(丙午)
论语有齐鲁论。
来谕得之。且在齐时所记。在鲁时所记。亦自不同。
孟子鸡豚狗彘之畜。
人家所畜。鸡豚狗彘之外。如牛羊并是常畜。似可为养老之物。然牛是诸侯之太牢而诸侯所无。故不杀者也。羊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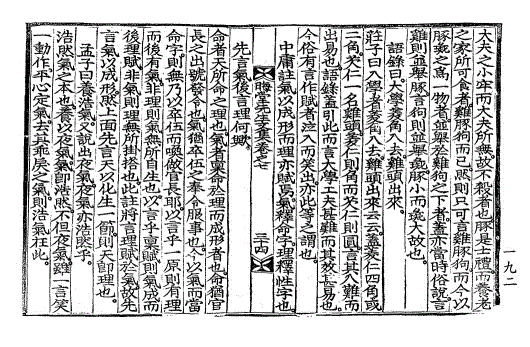 大夫之小牢而大夫所无。故不杀者也。豚是士礼。而养老之家所可食者。鸡豚狗而已。然则只可言鸡豚狗。而今以豚彘之为一物者。并举于鸡狗之下者。盖亦当时俗说。言鸡则并举豚。言狗则并举彘。豚小而彘大故也。
大夫之小牢而大夫所无。故不杀者也。豚是士礼。而养老之家所可食者。鸡豚狗而已。然则只可言鸡豚狗。而今以豚彘之为一物者。并举于鸡狗之下者。盖亦当时俗说。言鸡则并举豚。言狗则并举彘。豚小而彘大故也。语录曰。大学菱角入去。鸡头出来。
庄子曰入学者菱角入去。鸡头出来云云。盖菱仁四角或二角。芡仁一名鸡头。菱仁则角而芡仁则圆。言其入难而出易也。语录盖引此而言大学工夫甚难而其效甚易也。今俗有言作赋者泣入而笑出。亦此等之谓也。
中庸注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气释命字。理释性字也。先言气后言理何欤。
命者天所命之理也。气者禀命于理而成形者也。命犹官长之出号发令也。气犹卒伍之奉令服事也。今以气而当命字。则无乃以卒伍而唤做官长耶。以言乎一原则有理而后有气。非理则气无所自生也。以言乎禀赋则气成而后理赋。非气则理无所挂搭也。此注将言理赋于气。故先言气以成形。然上面先言天以化生一节。则天即理也。
孟子曰养浩气。又说出夜气。夜气亦浩然乎。
浩然气之本也。养以夜气。气即浩然。不但夜气。虽一言笑一动作。平心定气。去其乖戾之气。则浩气在此。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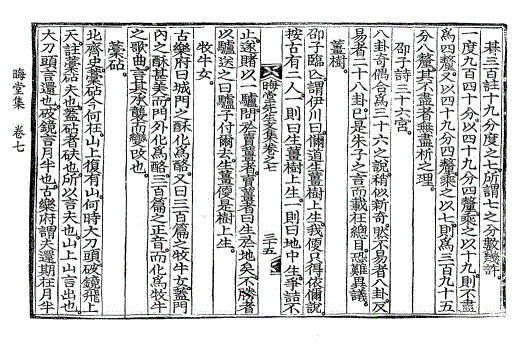 期三百注十九分度之七。所谓七之分数几许。
期三百注十九分度之七。所谓七之分数几许。一度九百四十分。以四十九分四釐。乘之以十九。则不尽为四釐。又以四十九分四釐。乘之以七。则为三百九十五分八釐。其不尽者无尽析之理。
邵子诗三十六宫。
八卦奇偶合为三十六之说。稍似新奇。然不易者八卦。反易者二十八卦。已是朱子之言而载在总目。恐难异议。
姜树。
邵子临亡。谓伊川曰。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便只得依你说。按古有二人。一则曰生姜树上生。一则曰地中生。争诘不止。遂赌以一驴。问于卖姜者。卖姜者曰生于地矣。不胜者以驴送之曰驴子付尔去。生姜便是树上生。
牧牛女。
古乐府曰城门之酥化为酪。又曰三百篇之牧牛女。盖门内之酥甚美。而门外化为酪。三百篇之正音。而化为牧牛之歌曲。言其承袭而变改也。
稿砧。
北齐史。稿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时大刀头。破镜飞上天。注稿砧夫也。盖砧者玞也。所以言夫也。山上山言出也。大刀头言还也。破镜言月半也。古乐府谓夫还期在月半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3L 页
 也。刀头有环故云。又按晋书。稿砧是农家捣草石。
也。刀头有环故云。又按晋书。稿砧是农家捣草石。赤蹄
韵书蹄蹄通。汉书赤蹄。注蹄犹纸也。染素纸令赤而书之。又按汉书。岳石阙铭高二丈二赤。王弇州曰赤与尺通。所以谓之赤牍也云云。盖尺书曰赤书。尺纸曰赤纸。
答郑聚五(载星○庚申)
贱身不禄。失我茶翁。思所以未尽于茶翁者。及于其朋徒之同志者。而如座下高明。死生契阔。未尝相闻。常所耿耿于怀。今奉牣幅示谕。其意甚勤。为之感谢而未已也。第审盛谕若将以世道之忧。交付于贱身者。是诚教僬而扛鼎也。春秋之世。乱贼横行。孟子之时。杨墨为祸。而以圣人许大力量。只是空言而配禹也。今日异教之为名。动以百数。虽有圣人手分。没柰他何。吾辈残命。只得死守孤城。誓不吞噬于强寇。而分付子弟后生。无或至于为降虏于蛮夷也。至若摧陷廓清之功。则惟俟皓天之返也。
答张进汝(丙午)
转褫得奉手谕。令人可读。可知其制作之工。亦遂长进。而只恨自乏金针。不能度与䲶机也。第念世变以来。才明通慧。可与有为者。皆以为读书无益。讨得别处去走。其下者冥然无意于此事。而贤明晚而觉悟。欲其不得而不措。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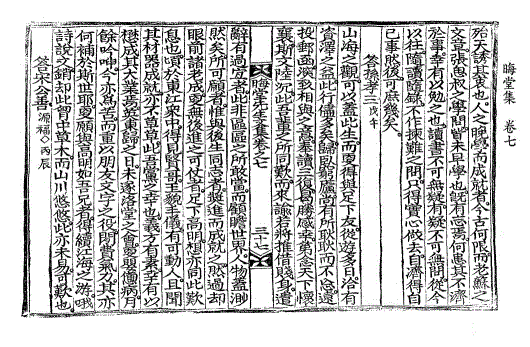 殆天诱其衷也。人之晚学而成就者。今古何限。而老苏之文章。张思叔之学问。皆未早学也。既有志焉。何患其不济于事。幸有以勉之也。读书不可无疑。有疑不可无问。从今以往。随读随录。不作拣难之问。只得实心做去。自济得自己事然后。可庶几矣。
殆天诱其衷也。人之晚学而成就者。今古何限。而老苏之文章。张思叔之学问。皆未早学也。既有志焉。何患其不济于事。幸有以勉之也。读书不可无疑。有疑不可无问。从今以往。随读随录。不作拣难之问。只得实心做去。自济得自己事然后。可庶几矣。答孙孝三(戊午)
山海之观。可以盖此生。而更得与足下友。从游多日。洽有资泽之益。此行尽多矣。归卧穷庐。尚有所耿耿而不忘。远投邮函。深致相与之意。奉读三复。曷胜感幸。第念天下怀襄。斯文陆沉。此吾辈之所同叹。而来谕若将推借贱身。遣辞有过宜者。此非区区之所敢当。而顾瞻世界。人物盖渺然矣。所可愿者。惟与后生同志者。奖进而成就之。然过却眼前诸老成。更无后进之可仗者。足下高明。想亦同此叹息也。顷于东江众中。得见贤哥。玉貌丰仪。有可动人。且闻其材器成就。亦不草草。此吾党之幸也。义方有素。幸有以懋成其大业焉。英东归之日。未遂洛堂之会。更婴惫病。月馀吟呻。今亦为苦。而重以朋友文字之役。閒费气力。其亦何补于斯世耶。更愿与高明如吾兄者。得续江海之游。哦诗说文。销却此胸中草木。而山川悠悠。此亦未易。可叹也。
答宋公善(源福○丙辰)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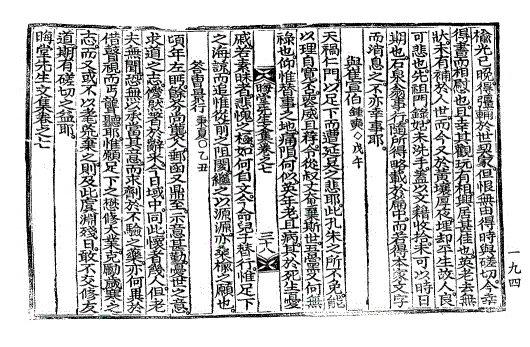 榆光已晚。得彊辅于世契家。但恨无由得时与磋切。今幸得书而相慰也。且幸其观玩有相。兴居甚佳也。英老去无状。未有补于人世。而今又于黄壤厚夜。埋却平生故人。良可悲也。先祖门录。姑未洗手。盖以文籍收拾。未可以时日期也。石泉翁事行。随所得略载于篇中。而若得本家文字而消息之。不亦幸事耶。
榆光已晚。得彊辅于世契家。但恨无由得时与磋切。今幸得书而相慰也。且幸其观玩有相。兴居甚佳也。英老去无状。未有补于人世。而今又于黄壤厚夜。埋却平生故人。良可悲也。先祖门录。姑未洗手。盖以文籍收拾。未可以时日期也。石泉翁事行。随所得略载于篇中。而若得本家文字而消息之。不亦幸事耶。与崔宣伯(钟奭○戊午)
天祸仁门。以足下而遭延吴之悲耶。此孔朱之所不免。能以理自宽否。丧威且荐。令从叔丈奄弃斯世。吾党又何无禄也。仰惟替事之地。痛陨何似。英年老且病。其于死生忧戚。若素昧者。悲愧之极。如何自文。今命儿子替行。惟足下之海谅。而追惟从前之阻阂。继之以源源。亦桑榆之愿也。
答曹景行(秉夏○乙丑)
顷年左眄。馀芬尚袭人。邮函又鼎至。示意甚勤。忧世之意。求道之志。僾然著于辞采。今日域中。同此怀者几人。但老夫无闻。恐无以承当其意。而求剂于不验之药。亦何异于借瞽视而丐聋听耶。惟愿足下之懋修大业。克励岁寒之志。而又或不以耄荒弃之。则及此虞渊残日。敢不交修友道。期有磋切之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