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书
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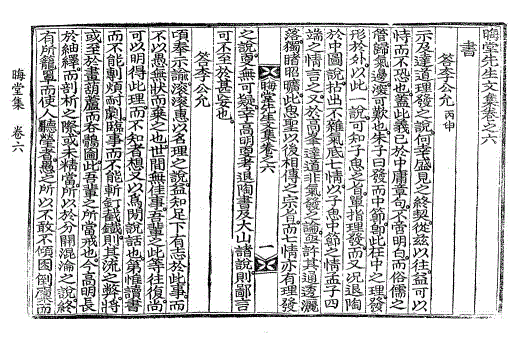 答李公允(丙申)
答李公允(丙申)示及达道理发之说。何幸盛见之终契。从玆以往。益可以恃而不恐也。盖此义已于中庸章句。不啻明白。而俗儒之管归气边。深可叹也。朱子曰发而中节。即此在中之理。发形于外。以此一说。可知子思之旨。单指理发。而又况退陶于中图说。拈出不杂气底七情。以子思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言之。又于高峰达道非气发之论。亟许其通透洒落。独睹昭旷。此思圣以后相传之宗旨。而七情亦有理发之说。更无可疑。幸高明更考退陶书及大山诸说。则鄙言可不至于甚妄也。
答李公允
顷奉示谕。滚滚惠以名理之说。益知足下有志于此事。而不以愚无状而弃之也。世间无佳事。吾辈之此等往复。尚可以明得此理。而不知者想又以为閒说话也。第惟读书而不能剸烦耐剧。临事而不能斩钉截铁。则其流之弊。将或至于画葫芦而吞鹘囵。此吾辈之所当戒也。今高明长于䌷绎。而剖析之际。或未精当。所以于分开混沦之说。终有所笼罩而使人听莹者。愚之所以不敢不倾囷倒廪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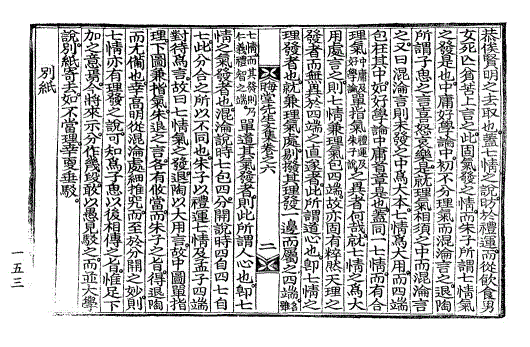 恭俟贤明之去取也。盖七情之说。昉于礼运。而从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上言之。此固气发之情。而朱子所谓七情气之发是也。中庸好学论中。初不分理气而混沦言之。退陶所谓子思之言喜怒哀乐。是就理气相须之中而混沦言之。又曰混沦言则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而四端包在其中。如好学论中庸首章是也。盖同一七情。而有合理气(中庸及好学论。)单指气(礼运及朱子说。)之异者何哉。就七情之为大用处言之。则七情兼理气包四端。故亦固有粹然天理之发者而无异于四端之直遂者。此所谓道心也。即七情之理发者也。就兼理气处。剔拨其理发一边而属之四端。(名虽七情。而其发则乃仁义礼智之端。)单道其气发者。则此所谓人心也。即七情之气发者也。混沦说时七包四。分开说时四自四七自七。此分合之所以不同也。朱子以礼运七情及孟子四端对待为言。故曰七情气之发。退陶以大用言。故中图单指理。下图兼指气。朱退之言。各有攸当。而朱子之旨。得退陶而尤备也。幸高明从混沦处细推究。而至于分开之妙。则七情亦有理发之说。可知为子思以后相传之旨。惟足下加之意焉。今将来示。分作几段。敢以愚见驳之。而并大学说。别纸寄去。如不当理。幸更垂驳。
恭俟贤明之去取也。盖七情之说。昉于礼运。而从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上言之。此固气发之情。而朱子所谓七情气之发是也。中庸好学论中。初不分理气而混沦言之。退陶所谓子思之言喜怒哀乐。是就理气相须之中而混沦言之。又曰混沦言则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而四端包在其中。如好学论中庸首章是也。盖同一七情。而有合理气(中庸及好学论。)单指气(礼运及朱子说。)之异者何哉。就七情之为大用处言之。则七情兼理气包四端。故亦固有粹然天理之发者而无异于四端之直遂者。此所谓道心也。即七情之理发者也。就兼理气处。剔拨其理发一边而属之四端。(名虽七情。而其发则乃仁义礼智之端。)单道其气发者。则此所谓人心也。即七情之气发者也。混沦说时七包四。分开说时四自四七自七。此分合之所以不同也。朱子以礼运七情及孟子四端对待为言。故曰七情气之发。退陶以大用言。故中图单指理。下图兼指气。朱退之言。各有攸当。而朱子之旨。得退陶而尤备也。幸高明从混沦处细推究。而至于分开之妙。则七情亦有理发之说。可知为子思以后相传之旨。惟足下加之意焉。今将来示。分作几段。敢以愚见驳之。而并大学说。别纸寄去。如不当理。幸更垂驳。别纸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4H 页
 平说喜怒哀乐则是混沦说。指达道言则已是理之发者。乃剔拨说。非混沦说也。盖子思之说出喜怒哀乐四字时。初不分理气。而以兼理气者混沦说也。自之未发以下。就兼理气处。单指其未发之理及已发之理而剔拨说也。达道只是七情之理发者。则此岂非七情亦有理发者乎。
平说喜怒哀乐则是混沦说。指达道言则已是理之发者。乃剔拨说。非混沦说也。盖子思之说出喜怒哀乐四字时。初不分理气。而以兼理气者混沦说也。自之未发以下。就兼理气处。单指其未发之理及已发之理而剔拨说也。达道只是七情之理发者。则此岂非七情亦有理发者乎。四端之曰理发。七情之曰气发。此是主分开而言也。四端自四端。七情自七情。固不可侵过界分。然而所谓七情之理发者。乃无异于四端。而自与气发底七情对待立说。则其界分甚明矣。盖尝言之。七情为大用。而就大用处言之。情之发岂七者而已哉。虽谓之千情万情。亦无不可。而特举其常情之易发者。名之曰七情。其实四端亦情也。戴记所谓五情。星湖所谓六情。栗谷所谓万般之情。皆是情也。情之为字。所包者甚广而为用甚大。故同是七情而有理发底情。亦有气发底情。所谓理发者。名虽七情而即道心也四端也。所谓气发者。即人心也七情也。今以一身体验而言之。见亲而喜。见赃吏而怒。见贤而爱。遭丧而哀。此是粹然天理之发而自不干气事也。又如男女之欲贫苦之恶。此是形气之发。而亦人之所不能无者也。今谓七情只是气发而初无理发。则子路闻过之喜。武王安天下之怒。孔子恸颜渊之哀。皆由于形气之私而非天理之发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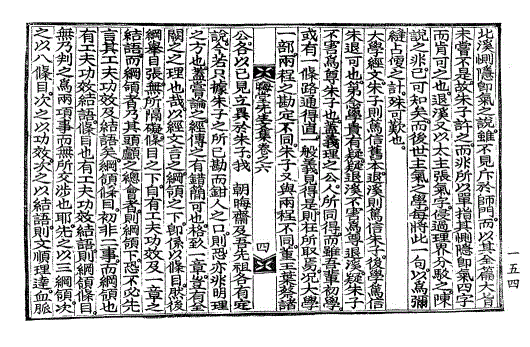 北溪恻隐即气之说。虽不见斥于师门。而以其全篇大旨未尝不是。故朱子许之。而非所以单指其恻隐即气四字而肯可之也。退溪又以太主张气字。侵过理界分驳之。陈说之非。已可知矣。而后世主气之学。每将此一句。以为弥缝占便之计。殊可叹也。
北溪恻隐即气之说。虽不见斥于师门。而以其全篇大旨未尝不是。故朱子许之。而非所以单指其恻隐即气四字而肯可之也。退溪又以太主张气字。侵过理界分驳之。陈说之非。已可知矣。而后世主气之学。每将此一句。以为弥缝占便之计。殊可叹也。大学经文。朱子则笃信旧本。退溪则笃信朱子。后学笃信朱退可也。第念学贵有疑。疑退溪不害为尊退溪。疑朱子不害为尊朱子也。盖义理之公。人所同得。而虽吾辈初学。或有一条路通得直。一般义见得是。则在所取焉。况大学一部。两程之勘定不同。朱子又与两程不同。董王叶蔡诸公。各以己见立异于朱子。我 朝晦斋及吾先祖各有定说。今若只据朱子之所已勘而钳人之口。则恐亦非明理之方也。盖尝论之。经传之有错简可也。格致一章。岂有全阙之之理也哉。以经文言之。纲领之下。即系以条目。然后纲举目张。无所隔碍。条目之下。自有工夫功效及一章之结语。而纲领者乃其头颅之总会者。则纲领下。恐不必先言其工夫功效及结语矣。纲领条目。初非二事。而纲领也有工夫功效结语。条目也有工夫功效结语。则纲领条目。无乃判之为两项事而无所交涉也耶。先之以三纲领。次之以八条目。次之以功效。次之以结语。则文顺理达。血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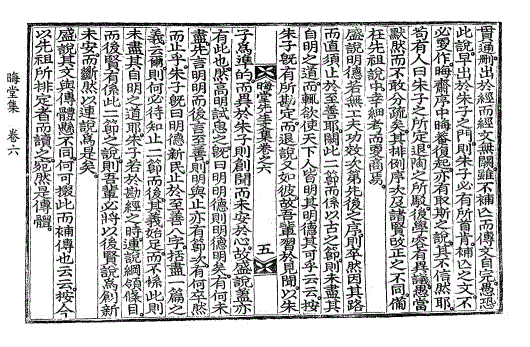 贯通。删出于经而经文无阙。虽不补亡而传文自完。愚恐此说。早出于朱子之门。则朱子必有所首肯。补亡之文。不必更作。晦斋序中晦庵复起。亦有取斯之说。其不信然耶。苟有人曰朱子之所定。退陶之所驳。后学容有异议。愚当默然而不敢分疏矣。其排例序次及诸贤改正之不同。备在先祖说中。幸细考而更商焉。
贯通。删出于经而经文无阙。虽不补亡而传文自完。愚恐此说。早出于朱子之门。则朱子必有所首肯。补亡之文。不必更作。晦斋序中晦庵复起。亦有取斯之说。其不信然耶。苟有人曰朱子之所定。退陶之所驳。后学容有异议。愚当默然而不敢分疏矣。其排例序次及诸贤改正之不同。备在先祖说中。幸细考而更商焉。盛说明德若无工夫功效次第先后之序。则卒然因其路而直须止于至善耶。阙此二节而系以古之节。则未尽其自明之道。而辄欲使天下人皆明其明德其可乎云云。按朱子既有所勘定。而退说又如彼。故吾辈习于见闻。以朱子为准的。而异于朱子则创闻而未安于心。故盛说盖亦有此也。然高明试思之。既曰明明德则明德明矣。有何未尽。先言明明而后言至善。则明与止亦有节次。有何卒然而止乎。朱子既曰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字。括尽一篇之义云尔。则何必待知止二节而后。其义始足。而不系此则未尽其自明之道耶。朱子若于勘经之时。连说纲领条目。而后贤有系此二节之说。则吾辈必将以后贤说为创新未安。而断然以连说为是矣。
盛说其文与传体悬不同。何可掇此而补传也云云。按今以先祖所排定者而读之。宛然是传体。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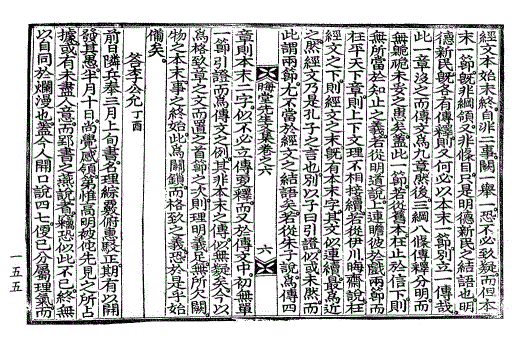 经文本始末终。自非二事。阙一举一。恐不必致疑。而但本末一节。既非纲领。又非条目。只是明德新民之结语也。明德新民。既各有传释。则又何必以本末一节。别立一传哉。此一章没之而传文为九章然后。三纲八条传释分明。而无臲卼未妥之患矣。盖此一节。若从旧本。在止于信下。则无所当于知止之义。若从明道说。上连瞻彼于戏两节而在平天下章。则上下文理不相接续。若从伊川,晦斋说。在经文之下。则经文之末。既有本末字。其文似连续。最为近之。然经文乃是孔子之言也。别以子曰引證。似或未然。而此谓两节。尤不当于经文之结语矣。若从朱子说。为传四章则本末二字。似不必立传更释。而又于传文中。初无单一节引證而为传文之例。其非本末之传。似无疑矣。今以为格致章之文而置之首节之次。则理明义足。无所欠阙。物之本末。事之终始。此为关锁。而格致之义。恐于是乎始备矣。
经文本始末终。自非二事。阙一举一。恐不必致疑。而但本末一节。既非纲领。又非条目。只是明德新民之结语也。明德新民。既各有传释。则又何必以本末一节。别立一传哉。此一章没之而传文为九章然后。三纲八条传释分明。而无臲卼未妥之患矣。盖此一节。若从旧本。在止于信下。则无所当于知止之义。若从明道说。上连瞻彼于戏两节而在平天下章。则上下文理不相接续。若从伊川,晦斋说。在经文之下。则经文之末。既有本末字。其文似连续。最为近之。然经文乃是孔子之言也。别以子曰引證。似或未然。而此谓两节。尤不当于经文之结语矣。若从朱子说。为传四章则本末二字。似不必立传更释。而又于传文中。初无单一节引證而为传文之例。其非本末之传。似无疑矣。今以为格致章之文而置之首节之次。则理明义足。无所欠阙。物之本末。事之终始。此为关锁。而格致之义。恐于是乎始备矣。答李公允(丁酉)
前日邻兵奉三月上旬书。名理综覈俯惠驳正。期有以开发其愚。半月十日。尚觉感领。第惟高明被佗先见之所占据。或有未尽人意。而郢书之燕说者。窃恐似此不已。终无以自同于烂漫也。盖今人开口说四七。便已分属理气。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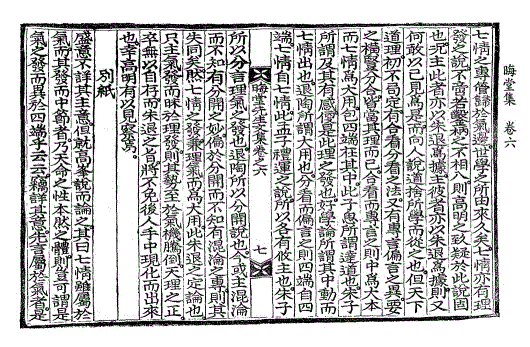 七情之专管归于气边。世学之所由来久矣。七情亦有理发之说。不啻若凿柄之不相入。则高明之致疑于此说固也。况主此者亦以朱退为据。主彼者亦以朱退为据。则又何敢以己见为是。而向人说道舍所学而从之也。但天下道理。初不局定。有合看分看之法。又有专言偏言之异。要之横竖分合。皆当其理而已。合看而专言之则中为大本而七情为大用。包四端在其中。此子思所谓达道也。朱子所谓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发也。好学论所谓其中动而七情出也。退陶所谓大用也。分看而偏言之则四端自四端。七情自七情。此孟子礼运之说。所以各有攸主也。朱子所以分言理气之发也。退陶所以分开说也。今或主混沦而不知有分开之妙。偏于分开而不知有混沦之专。则其失同矣。然七情之发。兼理气而为大用。此朱退之定论也。只主气发而昧于理发。则其势至于气机腾倒。天理之正。卒无以自存。而朱退之旨。将不免后人手中现化而出来也。幸高明有以见察焉。
七情之专管归于气边。世学之所由来久矣。七情亦有理发之说。不啻若凿柄之不相入。则高明之致疑于此说固也。况主此者亦以朱退为据。主彼者亦以朱退为据。则又何敢以己见为是。而向人说道舍所学而从之也。但天下道理。初不局定。有合看分看之法。又有专言偏言之异。要之横竖分合。皆当其理而已。合看而专言之则中为大本而七情为大用。包四端在其中。此子思所谓达道也。朱子所谓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发也。好学论所谓其中动而七情出也。退陶所谓大用也。分看而偏言之则四端自四端。七情自七情。此孟子礼运之说。所以各有攸主也。朱子所以分言理气之发也。退陶所以分开说也。今或主混沦而不知有分开之妙。偏于分开而不知有混沦之专。则其失同矣。然七情之发。兼理气而为大用。此朱退之定论也。只主气发而昧于理发。则其势至于气机腾倒。天理之正。卒无以自存。而朱退之旨。将不免后人手中现化而出来也。幸高明有以见察焉。别纸
盛意不详其主意。但就高峰说而论之。其曰七情虽属于气。而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则岂可谓是气之发而异于四端乎云云。窃详其意。先言属于气者。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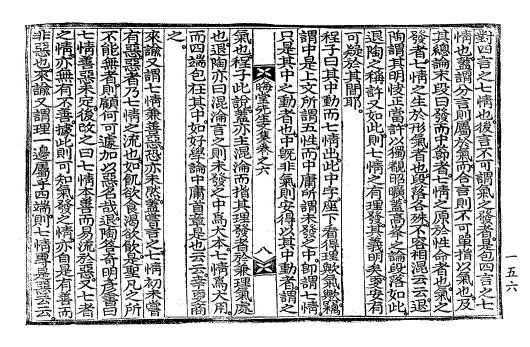 对四言之七情也。后言不可谓气之发者。是包四言之七情也。盖谓分言则属于气。而合言则不可单指以气也。及其总论末段曰发而中节者。七情之原于性命者也。气之发者。七情之生于形气者也。段落各殊。不容相混云云。退陶谓其明快正当。许以独睹昭旷。盖高峰之论段落如此。退陶之称许又如此。则七情之有理发。其义明矣。更安有可疑于其间耶。
对四言之七情也。后言不可谓气之发者。是包四言之七情也。盖谓分言则属于气。而合言则不可单指以气也。及其总论末段曰发而中节者。七情之原于性命者也。气之发者。七情之生于形气者也。段落各殊。不容相混云云。退陶谓其明快正当。许以独睹昭旷。盖高峰之论段落如此。退陶之称许又如此。则七情之有理发。其义明矣。更安有可疑于其间耶。程子曰其中动而七情出。此中字。座下看得理欤气欤。窃谓中是上文所谓五性。而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即谓七情。只是其中之动者也。中既非气则安得以其中动者。谓之气也。程子此说。盖亦主混沦而指其理发者于兼理气处也。退陶亦曰混沦言之则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而四端包在其中。如好学论中庸首章是也云云。幸更商之。
来谕又谓七情兼善恶。恐亦未然。盖尝言之。七情初未尝有恶。恶者乃七情之流也。如饥欲食渴欲饮。是圣凡之所不能无者。则顾何可遽加以恶名哉。退陶答奇明彦书曰七情善恶未定。后改之曰七情本善而易流于恶。又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据此则可知气发之情。亦自是有善而非恶也。来谕又谓理一边属乎四端。则七情专是恶云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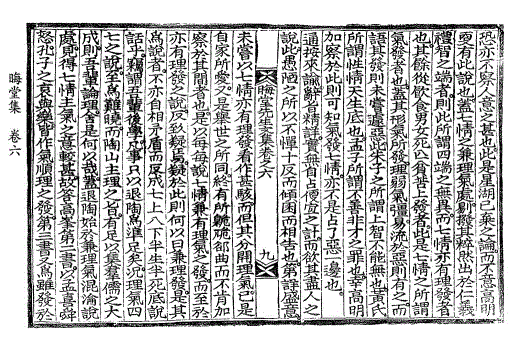 恐亦不察人意之甚也。此是星湖已弃之论。而不意高明更有此说也。盖七情之兼理气处。剔拨其粹然出于仁义礼智之端者。则此所谓四端之无异。而七情亦有理发者也。其馀从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上发者。此是七情之所谓气发者也。盖其形气所发。理弱气彊。易流于恶则有之。而语其发则未尝遽恶。此朱子之所谓上智不能无也。黄氏所谓性情天生底也。孟子所谓不善非才之罪也。幸高明加察于此则可知气发七情。亦不是占了恶一边也。
恐亦不察人意之甚也。此是星湖已弃之论。而不意高明更有此说也。盖七情之兼理气处。剔拨其粹然出于仁义礼智之端者。则此所谓四端之无异。而七情亦有理发者也。其馀从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上发者。此是七情之所谓气发者也。盖其形气所发。理弱气彊。易流于恶则有之。而语其发则未尝遽恶。此朱子之所谓上智不能无也。黄氏所谓性情天生底也。孟子所谓不善非才之罪也。幸高明加察于此则可知气发七情。亦不是占了恶一边也。通按来谕。辞旨精详。实无自占便宜之计。而欲其尽人之说。此愚陋之所以不惮十反而倾囷而相告也。第详盛意。未尝以七情亦有理发看作甚骇。而但其分开理气。已是自家所爱。又是举世之所同。终有所臲卼郤曲而不肯加察于其间者也。是以每每说七情兼有理气之发。而至于亦有理发之说。反致疑焉。疑于此则何以曰兼理发。是其为说者。不亦自相矛盾而反成七上八下半生半死底说话乎。窃谓吾辈后学。凡事只以退陶为准足矣。况理气四七之说。至为难晓。而陶山主理之旨。有足以集群儒之大成。则吾辈论理。舍是何以哉。盖退陶始于兼理气混沦说处。见得七情主气之意较甚。故答高峰第二书。以孟喜舜怒。孔子之哀与乐。皆作气顺理之发。第三书又为虽发于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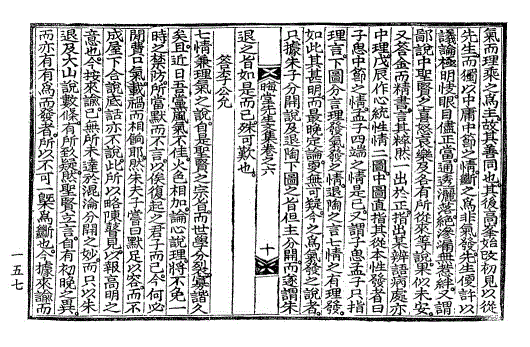 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其后高峰始改初见以从先生。而独以中庸中节之情。断之为非气发。先生便许以议论极明快。眼目尽正当。通透洒落。绝渗漏无惹绊。又谓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未安。又答金而精书。言其粹然一出于正。指出某辨语病处亦中理。戊辰作心统性情二图。中图直指其从本性发者曰子思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是已。又谓子思孟子只指理言。下图分言理发气发之情。退陶之言七情之有理发。如此其甚明。而最晚定论。更无可疑。今之为气发之说者。只据朱子分开说及退陶下图之旨但主分开。而遂谓朱退之旨如是而已。殊可叹也。
气而理乘之为主。故其善同也。其后高峰始改初见以从先生。而独以中庸中节之情。断之为非气发。先生便许以议论极明快。眼目尽正当。通透洒落。绝渗漏无惹绊。又谓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未安。又答金而精书。言其粹然一出于正。指出某辨语病处亦中理。戊辰作心统性情二图。中图直指其从本性发者曰子思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是已。又谓子思孟子只指理言。下图分言理发气发之情。退陶之言七情之有理发。如此其甚明。而最晚定论。更无可疑。今之为气发之说者。只据朱子分开说及退陶下图之旨但主分开。而遂谓朱退之旨如是而已。殊可叹也。答李公允
七情兼理气之说。自是圣贤之宗旨。而世学分裂。寡谐久矣。且近日吾党风气不佳。火色相加。论心说理。将不免一时之禁防。所当默而不言。以俟复起之君子而已。今何必閒费口气。载祸而相饷耶。然朱夫子尝曰默足以容。而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说。此所以略陈瞽见。以报高明之意也。今按来谕。已无所未达于混沦分开之妙。而只以朱退及大山说数条。有所致疑。然圣贤立言。自有初晚之异。而亦有有为而发者。所以不可一槩为断也。今据来谕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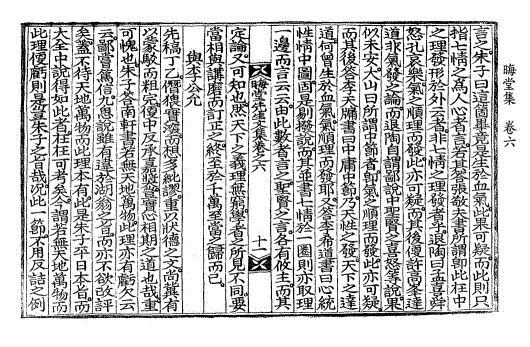 言之。朱子曰这个毕竟是生于血气。此果可疑。而此则只指七情之为人心者言。若其答张敬夫书所谓即此在中之理发形于外云者。非七情之理发者乎。退陶曰孟喜舜怒孔哀乐。气之顺理而发。此亦可疑。而其后便许高峰达道非气发之论。而退陶自谓鄙说中圣贤之喜怒等说。果似未安。大山曰所谓中节者。即气之顺理而发。此亦可疑。而其后答李天牖书曰中庸中节。乃天性之发。天下之达道。何曾生于血气。气顺理而发耶。又答李希道书曰心统性情中图。固是剔拨说。而其并书七情于一圈则亦取理一边而言云云。由此数者言之。圣贤之言。各有攸主。而其定论。又可知也。然天下之义理无穷。学者之所见不同。要当相与讲磨而订正之。终至于千万至当之归而已。
言之。朱子曰这个毕竟是生于血气。此果可疑。而此则只指七情之为人心者言。若其答张敬夫书所谓即此在中之理发形于外云者。非七情之理发者乎。退陶曰孟喜舜怒孔哀乐。气之顺理而发。此亦可疑。而其后便许高峰达道非气发之论。而退陶自谓鄙说中圣贤之喜怒等说。果似未安。大山曰所谓中节者。即气之顺理而发。此亦可疑。而其后答李天牖书曰中庸中节。乃天性之发。天下之达道。何曾生于血气。气顺理而发耶。又答李希道书曰心统性情中图。固是剔拨说。而其并书七情于一圈则亦取理一边而言云云。由此数者言之。圣贤之言。各有攸主。而其定论。又可知也。然天下之义理无穷。学者之所见不同。要当相与讲磨而订正之。终至于千万至当之归而已。与李公允
先稿丁乙。僭猥实深。而想多纰谬。重以状德之文。尚冀有以蒙驳而粗完。便中反承嘉奖。岂实心相期之道也哉。重可愧也。朱子答南轩书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云云。鄙尝笃信。九思说虽有违于湖翁之旨。而亦不欲改评矣。盖不待天地万物而此理本有。此是朱子平日本旨。而大全中说得如此者。在在可考矣。今谓若无天地万物而此理便亏则是岂朱子之旨哉。况此一节。不用反诘之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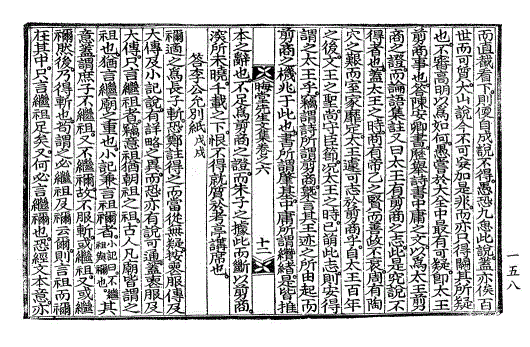 而直截看下。则便自成说不得。愚恐九思此说。盖亦俟百世而可质。大山说今不可妄加是非。而亦只得阙其所疑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愚尝于大全中最有可疑。即太王剪商事也。答陈安卿书。历举诗书中庸之文。以为太王剪商之證。而论语集注又曰太王有剪商之志。此是究说不得者也。盖太王之时。商有帝乙之贤而善政不衰。周有陶穴之艰而室家靡定。太王遽可志于剪商乎。自太王百年之后。文王之圣。尚守臣节。况太王之时。已萌此志。则安得谓之太王乎。窃谓诗所谓剪商。槩言其王迹之所由起而剪商之机兆于此也。书所谓肇基。中庸所谓缵绪。是皆推本之辞也。不足为剪商之證。而朱子之据此而断以剪商。深所未晓。千载之下。恨不得就质于考亭讲席也。
而直截看下。则便自成说不得。愚恐九思此说。盖亦俟百世而可质。大山说今不可妄加是非。而亦只得阙其所疑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愚尝于大全中最有可疑。即太王剪商事也。答陈安卿书。历举诗书中庸之文。以为太王剪商之證。而论语集注又曰太王有剪商之志。此是究说不得者也。盖太王之时。商有帝乙之贤而善政不衰。周有陶穴之艰而室家靡定。太王遽可志于剪商乎。自太王百年之后。文王之圣。尚守臣节。况太王之时。已萌此志。则安得谓之太王乎。窃谓诗所谓剪商。槩言其王迹之所由起而剪商之机兆于此也。书所谓肇基。中庸所谓缵绪。是皆推本之辞也。不足为剪商之證。而朱子之据此而断以剪商。深所未晓。千载之下。恨不得就质于考亭讲席也。答李公允别纸(戊戌)
祢适之为长子斩。恐郑注得之而当从无疑。按丧服传及大传及小记说。有详略之异。而恐亦有说可通。盖丧服及大传。只言继祖者。窃意祖犹朝祖之祖。古人凡庙皆谓之祖也。犹言继庙之重也。小记兼言祖祢者。(小记曰。不继祖与祢也。)其意盖谓庶子不继祖。又不继祢。故不服斩。或继祖。又或继祢然后。乃得斩也。苟谓之必继祖及祢云尔。则言祖而祢在其中。只言继祖足矣。又何必言继祢也。恐经文本意。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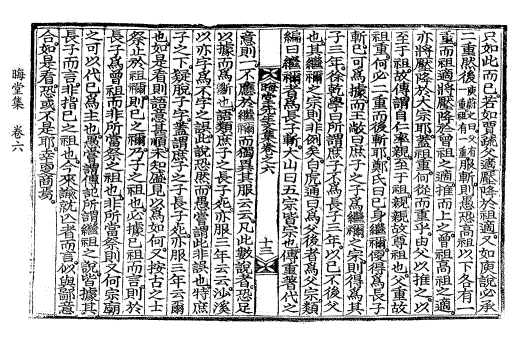 只如此而已。若如贾疏父适压降于祖适。又如庾说必承二重然后(庾蔚之曰。父有一重。祖有一重。)服斩。则愚恐高祖以下各有一重。而祖适将压降于曾祖之适。推而上之。曾祖高祖之适。亦将压降于大宗耶。盖祖重。何从而重乎。由父以推之。以至于祖。故传谓自仁率亲。至于祖。亲亲故尊祖也。父重故祖重。何必二重而后斩耶。郑氏曰己身继祢。便得为长子斩。已可为据。而王敞曰庶子之子为继祢之宗。则得为其子三年。徐乾学曰所谓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以己不后父也。其继祢之宗则非例矣。白虎通曰为父后者为父宗。类编曰继祢者为长子斩。大山曰五宗皆宗也。传重著代之意则一。不应于继祢而独异其服云云。凡此数说者。恐足以据而为断也。语类庶子之长子死。亦服三年云云。沙溪以亦字为不字之误。此说恐然。而愚尝谓此非误也。特庶子之下。疑脱子字。盖谓庶子之子长子死。亦服三年云尔也。如是看则语意甚顺。未知盛见以为如何。又按古之士祭止于祖祢。则己之祢。乃子之祖也。必据己祖而言。则于长子为曾祖而非所当祭之祖也。非所当祭则又何宗庙之可以代己为主也。愚尝谓传记所谓继祖之说。皆据其长子而言。非指己之祖也。今来谕就亡者而言。似与鄙意合。如是看。恐或不是耶。幸更商焉。
只如此而已。若如贾疏父适压降于祖适。又如庾说必承二重然后(庾蔚之曰。父有一重。祖有一重。)服斩。则愚恐高祖以下各有一重。而祖适将压降于曾祖之适。推而上之。曾祖高祖之适。亦将压降于大宗耶。盖祖重。何从而重乎。由父以推之。以至于祖。故传谓自仁率亲。至于祖。亲亲故尊祖也。父重故祖重。何必二重而后斩耶。郑氏曰己身继祢。便得为长子斩。已可为据。而王敞曰庶子之子为继祢之宗。则得为其子三年。徐乾学曰所谓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以己不后父也。其继祢之宗则非例矣。白虎通曰为父后者为父宗。类编曰继祢者为长子斩。大山曰五宗皆宗也。传重著代之意则一。不应于继祢而独异其服云云。凡此数说者。恐足以据而为断也。语类庶子之长子死。亦服三年云云。沙溪以亦字为不字之误。此说恐然。而愚尝谓此非误也。特庶子之下。疑脱子字。盖谓庶子之子长子死。亦服三年云尔也。如是看则语意甚顺。未知盛见以为如何。又按古之士祭止于祖祢。则己之祢。乃子之祖也。必据己祖而言。则于长子为曾祖而非所当祭之祖也。非所当祭则又何宗庙之可以代己为主也。愚尝谓传记所谓继祖之说。皆据其长子而言。非指己之祖也。今来谕就亡者而言。似与鄙意合。如是看。恐或不是耶。幸更商焉。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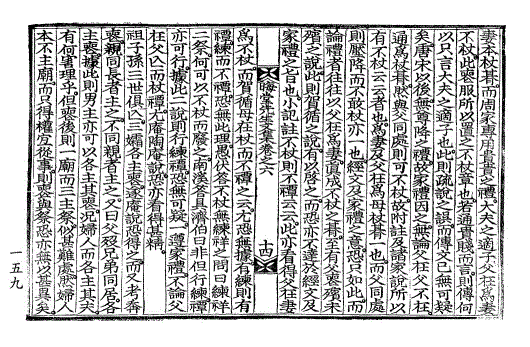 妻本杖期。而周家专用贵贵之礼。大夫之适子父在为妻不杖。此丧服所以置之不杖章也。若通贵贱而言。则传何以只言大夫之适子也。此则疏说之误。而传文已无可疑矣。唐宋以后。无尊降之礼。故家礼因之。无论父在父不在。通为杖期。然与父同处则可不杖。故附注及诸家说所以有不杖云云者也。为妻及父在为母杖期一也。而父同处则压降而不敢杖亦一也。经文及家礼之意。恐只如此。而论礼者往往以父在为妻。真成不杖之期。至有父丧殡未殡之说。此则贺循之说。有以启之。而恐亦不达于经文及家礼之旨也。小记注不杖则不禫云云。此亦看得父在妻为不杖。而贺循母在杖而不禫之云。尤恐无据。有练则有禫。练而不禫。恐无此理。愚伏答不杖无练祥之问曰练祥二祭。何可以不杖而废之。南溪答具济伯曰非但行练。禫亦可行。据此二说则行练禫。恐无可疑。一遵家礼。不论父在父亡而杖禫。尤庵陶庵说。恐亦看得甚精。
妻本杖期。而周家专用贵贵之礼。大夫之适子父在为妻不杖。此丧服所以置之不杖章也。若通贵贱而言。则传何以只言大夫之适子也。此则疏说之误。而传文已无可疑矣。唐宋以后。无尊降之礼。故家礼因之。无论父在父不在。通为杖期。然与父同处则可不杖。故附注及诸家说所以有不杖云云者也。为妻及父在为母杖期一也。而父同处则压降而不敢杖亦一也。经文及家礼之意。恐只如此。而论礼者往往以父在为妻。真成不杖之期。至有父丧殡未殡之说。此则贺循之说。有以启之。而恐亦不达于经文及家礼之旨也。小记注不杖则不禫云云。此亦看得父在妻为不杖。而贺循母在杖而不禫之云。尤恐无据。有练则有禫。练而不禫。恐无此理。愚伏答不杖无练祥之问曰练祥二祭。何可以不杖而废之。南溪答具济伯曰非但行练。禫亦可行。据此二说则行练禫。恐无可疑。一遵家礼。不论父在父亡而杖禫。尤庵陶庵说。恐亦看得甚精。祖子孙三世俱亡。三孀各主丧。遂庵说恐得之。而又考奔丧。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又曰父殁兄弟同居。各主丧。据此则男主亦可以各主其丧。况妇人而各主其夫。有何害理乎。但丧后则一庙而三主祭。似甚难处。然妇人本不主庙。而只得权宜从事。则丧与祭恐亦无以甚异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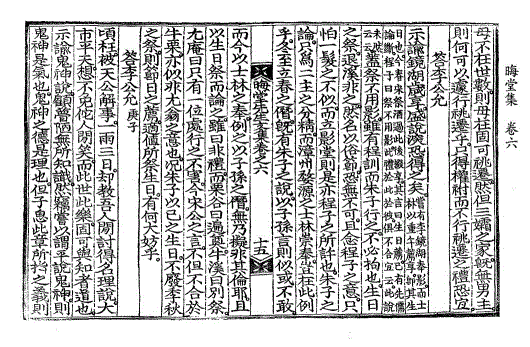 母不在世数。则母在固可祧迁。然但三孀之家。既无男主。则何可以遽行祧迁乎。只得权祔而不行祧迁之礼恐宜。
母不在世数。则母在固可祧迁。然但三孀之家。既无男主。则何可以遽行祧迁乎。只得权祔而不行祧迁之礼恐宜。答李公允
示谕镜湖岁享。盛说深恐得之矣。(尝有李镜湖奉影。而士林以重午荐享。即其生日也。今春宋祭酒过此后掇享。其言曰生日荐。已有先儒论断。程子曰祭不用影。此礼于此于彼。俱不合宜云。此说未然云云。)盖祭不用影。虽有程训而朱子行之。不必拘也。生日之祭。退溪非之。然名以俗节。恐无不可。且念程子之意。只怕一发之不似。而立影堂则是亦程子之所许也。朱子之论。只为二主之分精。而漳州婺源之士林崇奉。岂在此例乎。冬至立春之僭。既有朱子之说。以子孙言则似或不敢。而今以士林之奉。例之以子孙之僭。无乃拟非其伦耶。且以生日祭而论之。虽曰非礼。而栗谷曰遍奠。牛溪曰别祭。尤庵曰只有一位处行之不害。今宋公之言。不但不合于牛栗。亦似非尤翁之意也。况朱子以己之生日。不废季秋之祭。则节日之荐。适值所祭生日。有何大妨乎。
答李公允(庚子)
顷枉。被天公解事。一雨三日。却教吾人閒讨得名理说。大市平天。想不免佗人閒笑。而此世此乐。固可与知者道也。示谕鬼神说。顾瞢陋无所知识。然窃尝以谓平说鬼神。则鬼神是气也。鬼神之德是理也。但子思此章所指之义则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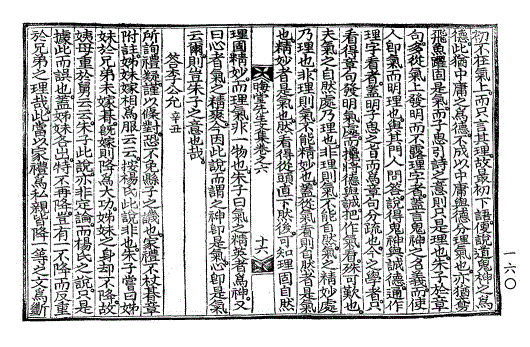 初不在气上。而只言其理。故最初下语。便说道鬼神之为德。此犹中庸之为德。不成以中庸与德分理气也。亦犹鸢飞鱼跃固是气。而子思引诗之意则只是理也。朱子于章句。多从气上发明而不露理字者。盖言鬼神之名义。而使人即气而明理也。与其门人问答。说得鬼神与诚德。通作理字看者。盖明子思之旨而为章句分疏也。今之学者。只看得章句发明气处。而搀将德与诚。把作气看。殊可叹也。夫气之自然处乃理也。非理则气不能自然。气之精妙处乃理也。非理则气不能精妙也。盖从气看则自然者是气也。精妙者是气也。然看得从头直下然后。可知理固自然理固精妙。而理气非一物也。朱子曰气之精英者为神。又曰心者气之精爽。今因此说而谓之神即是气。心即是气云尔。则岂朱子之意也哉。
初不在气上。而只言其理。故最初下语。便说道鬼神之为德。此犹中庸之为德。不成以中庸与德分理气也。亦犹鸢飞鱼跃固是气。而子思引诗之意则只是理也。朱子于章句。多从气上发明而不露理字者。盖言鬼神之名义。而使人即气而明理也。与其门人问答。说得鬼神与诚德。通作理字看者。盖明子思之旨而为章句分疏也。今之学者。只看得章句发明气处。而搀将德与诚。把作气看。殊可叹也。夫气之自然处乃理也。非理则气不能自然。气之精妙处乃理也。非理则气不能精妙也。盖从气看则自然者是气也。精妙者是气也。然看得从头直下然后。可知理固自然理固精妙。而理气非一物也。朱子曰气之精英者为神。又曰心者气之精爽。今因此说而谓之神即是气。心即是气云尔。则岂朱子之意也哉。答李公允(辛丑)
所询礼疑。谨以条对。恐不免县子之讥也。家礼不杖期章附注。姊妹嫁相为服云云。按杨氏此说非也。朱子尝曰姊妹于兄弟未嫁期。既嫁则降为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故姨母重于舅云云。朱子此说。亦非定论。而杨氏之说。只是据此而误也。盖姊妹各出。特不再降。岂有一不降而反重于兄弟之理哉。此当以家礼为私亲皆降一等之文为断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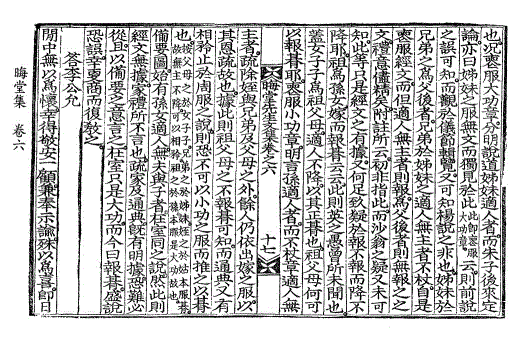 也。况丧服大功章。分明说道姊妹适人者。而朱子后来定论。亦曰姊妹之服无文而独见于此(此即丧服大功章。)云。则前说之误可知。而观于仪节辑览。又可知杨说之非也。姊妹于兄弟之为父后者。兄弟于姊妹之适人无主者不杖。自是丧服经文。而但适人无主者则报。为父后者则无报之之文。礼意尽精矣。附注所云。初非指此。而沙翁之疑又未可知。此等只是经文之有据。又何足致疑于报不报而降不降耶。祖为孙女。嫁而报期云云。此则英之愚曾所未闻也。盖女子子为祖父母。适人不降。以其正期也。祖父母何可以报期耶。丧服小功章。明言孙适人者。而不杖章适人无主者。疏除侄与兄弟及父母之外。馀人仍依出嫁之服。以其恩疏故也。据此则祖父母之不报期可知。而通典又有相矜止于周服之说。则恐不可以小功之服而推之以期也。(按父母之于女子子。兄弟之于姊妹。侄之于姑本服期。故无主不降。可以相矜。祖之于孙。本服是大功故也。)备要图。始有孙女适人。无夫与子者。在室同之说。然此则经文无据。家礼所不言也。疏家及通典。既有明据。恐难必从。且以备要之意言之。在室只是大功。而今曰报期。盛说恐误。幸更商而复教之。
也。况丧服大功章。分明说道姊妹适人者。而朱子后来定论。亦曰姊妹之服无文而独见于此(此即丧服大功章。)云。则前说之误可知。而观于仪节辑览。又可知杨说之非也。姊妹于兄弟之为父后者。兄弟于姊妹之适人无主者不杖。自是丧服经文。而但适人无主者则报。为父后者则无报之之文。礼意尽精矣。附注所云。初非指此。而沙翁之疑又未可知。此等只是经文之有据。又何足致疑于报不报而降不降耶。祖为孙女。嫁而报期云云。此则英之愚曾所未闻也。盖女子子为祖父母。适人不降。以其正期也。祖父母何可以报期耶。丧服小功章。明言孙适人者。而不杖章适人无主者。疏除侄与兄弟及父母之外。馀人仍依出嫁之服。以其恩疏故也。据此则祖父母之不报期可知。而通典又有相矜止于周服之说。则恐不可以小功之服而推之以期也。(按父母之于女子子。兄弟之于姊妹。侄之于姑本服期。故无主不降。可以相矜。祖之于孙。本服是大功故也。)备要图。始有孙女适人。无夫与子者。在室同之说。然此则经文无据。家礼所不言也。疏家及通典。既有明据。恐难必从。且以备要之意言之。在室只是大功。而今曰报期。盛说恐误。幸更商而复教之。答李公允
閒中无以为怀。幸得敬安一顾。兼奉示谕。殊以为喜。即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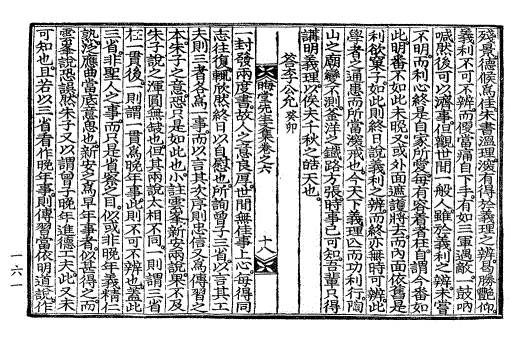 残景。德候为佳。朱书温理。深有得于义理之辨。曷胜艳仰。义利不可不辨。而便当痛自下手。有如三军遇敌。一鼓呐喊然后可以济事。但观世间一般人。虽于义利之辨。未尝不明。而利心终是自家所爱。每有容着者在。自谓今番如此。明番不如此未晚。又或外面遮护将去。而内面依旧是利欲窠子。如此则终日说义利之辨。而终亦无时可辨。此学者之通患而所当深戒也。今天下义理亡而功利行。陶山之庙变不测。釜洋之铁路方张。时事已可知。吾辈只得讲明义理。以俟夫千秋之皓天也。
残景。德候为佳。朱书温理。深有得于义理之辨。曷胜艳仰。义利不可不辨。而便当痛自下手。有如三军遇敌。一鼓呐喊然后可以济事。但观世间一般人。虽于义利之辨。未尝不明。而利心终是自家所爱。每有容着者在。自谓今番如此。明番不如此未晚。又或外面遮护将去。而内面依旧是利欲窠子。如此则终日说义利之辨。而终亦无时可辨。此学者之通患而所当深戒也。今天下义理亡而功利行。陶山之庙变不测。釜洋之铁路方张。时事已可知。吾辈只得讲明义理。以俟夫千秋之皓天也。答李公允(癸卯)
一封发两度书。故人之意良厚。世间无佳事上心。每得同志往复。辄欣然终日以自慰也。所询曾子三省。以言其工夫则三者各为一事。而以言其次序则忠信又为传习之本。朱子之意。恐只是如此也。小注云峰,新安两说。果不及朱子说之浑圆无缺也。但其两说太相不同。一则谓三省在一贯后。一则谓一贯为晚年事。此则不可不辨也。盖此三省。非圣人之事。而只是省察之目。似或非晚年义精仁熟。泛应曲当底意思也。新安之为早年事者。似甚得之。而云峰说恐误。然朱子又以谓曾子晚年进德工夫。此又未可知也。且若以三省看作晚年事。则传习当依明道说。作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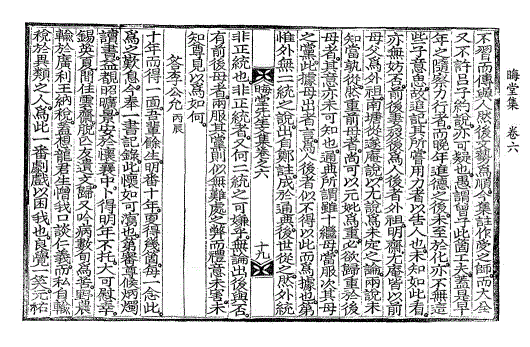 不习而传与人然后文势为顺。今集注作受之师。而大全又不许吕子约说。亦可疑也。愚谓曾子此个工夫。盖是早年之随察力行者。而晚年进德之后。未至于化。亦不无这些子意思。故追记其所尝用力者以告人也。未知如此看。亦无妨否。前后妻殁后为人后者外祖。明斋,尤庵皆以前母父为外祖。南塘从遂庵说。以尤说为未定之论。两说未知当孰从。然重前母者。尚可以元妣为重。必欲归重于后母者。其意亦未可知也。通典所谓虽十继母。当服次其母之党。此据母出者言。为人后者似不得以此而为据也。第惟外无二统之说。出自郑注。成于通典。后世从之。然外统非正统也。非正统者。又何二统之可嫌乎。无论出后与否。有前后母者。两服其党则似无难处之弊而礼意未害。未知尊见以为如何。
不习而传与人然后文势为顺。今集注作受之师。而大全又不许吕子约说。亦可疑也。愚谓曾子此个工夫。盖是早年之随察力行者。而晚年进德之后。未至于化。亦不无这些子意思。故追记其所尝用力者以告人也。未知如此看。亦无妨否。前后妻殁后为人后者外祖。明斋,尤庵皆以前母父为外祖。南塘从遂庵说。以尤说为未定之论。两说未知当孰从。然重前母者。尚可以元妣为重。必欲归重于后母者。其意亦未可知也。通典所谓虽十继母。当服次其母之党。此据母出者言。为人后者似不得以此而为据也。第惟外无二统之说。出自郑注。成于通典。后世从之。然外统非正统也。非正统者。又何二统之可嫌乎。无论出后与否。有前后母者。两服其党则似无难处之弊而礼意未害。未知尊见以为如何。答李公允(丙辰)
十年而得一面。吾辈馀生。明番十年。更得几个。每一念此。为之叹息。今奉一书记录。此怀如可泻也。第审尊候炳烛读书。益睹昭旷。景安于怀襄中。卜得明年不托。大可慰幸。锡英夏间住云斋。脱亡友遗文。归又吟病数旬为苦。野农输于广利王纳税。盖想龙君生憎我口谈仁义。而私自输税于异类之人。为此一番剧戏以困我也。良觉一笑。元祐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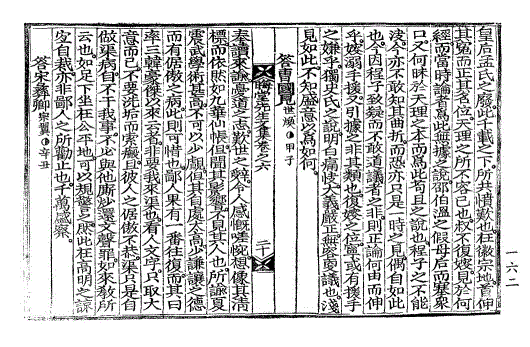 皇后孟氏之废。此千载之下。所共愤叹也。在徽宗地。首伸其冤而正其名位。天理之所不容已也。叔不复嫂。见于何经。而当时论者为此无据之说。邵伯温之假母后而塞众口。又何昧于天理之本而为此苟且之说也。程子之不能决。今亦不敢知其曲折。而恐亦只是一时之见。偶自如此也。今因程子致疑而不敢道议者之非。则正论何由而伸乎。嫂溺手援。又引据之非其类也。复嫂之位。宁或有援手之嫌乎。独史氏之说。明白痛快。大义严正。无容更议也。浅见如此。不知盛意以为如何。
皇后孟氏之废。此千载之下。所共愤叹也。在徽宗地。首伸其冤而正其名位。天理之所不容已也。叔不复嫂。见于何经。而当时论者为此无据之说。邵伯温之假母后而塞众口。又何昧于天理之本而为此苟且之说也。程子之不能决。今亦不敢知其曲折。而恐亦只是一时之见。偶自如此也。今因程子致疑而不敢道议者之非。则正论何由而伸乎。嫂溺手援。又引据之非其类也。复嫂之位。宁或有援手之嫌乎。独史氏之说。明白痛快。大义严正。无容更议也。浅见如此。不知盛意以为如何。答曹国见(世焕○甲子)
奉读来谕。忧道之志。叹世之辞。令人感慨嗟惋。想像其清标。而依然如九华仙帐。但闻其影响。不见其人也。所谕夏震武学术甚高。不可以少觑。但其自处太高。少谦让之德而有倨傲之病。此则可惜也。鄙人果有一番往复。而其曰率三韩豪杰以来云者。非要我来渠也。看人文字。只取大意而已。不要洗垢而索瘢。且彼人之倨傲不恭。渠只是自做渠病。自不干我事。不必与他厮炒还文声罪。如来教所云也。如足下坐在公平地。可以规警之。然此在高明之谅宜自裁。亦非鄙人之所劝止也。千万盛察。
答宋彝卿(宗翼○辛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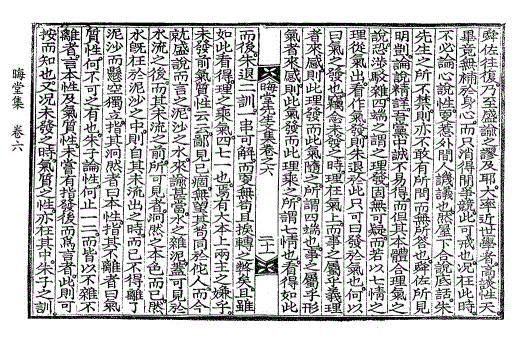 舜佐往复。乃至盛谕之谬及耶。大率近世学者。高谈性天。毕竟无补于身心。而只消得閒争竞。此可戒也。况在此时。不必论心说性。更惹外间人讥议也。然屋下合说底话。朱先生之所不禁。则亦不敢有所问而无所答也。舜佐所见明剀。论说精详。吾党中诚不易得。而但其本体合理气之说。恐涉驳杂。四端之谓之理发。固无可疑。而若以七情之理从气出。看作气发。则朱退于此只可曰发于气也。何以曰气之发也。窃念未发之时。理在气上。而事之属乎义理者来感。则此理发而此气随之。所谓四端也。事之属乎形气者来感。则此气发而此理乘之。所谓七情也。看得如此而后。朱退二训。一串可解。而更无苟且捩转之弊矣。且虽如此看得。理之乘气。四七一也。焉有大本上两主之嫌乎。未发前气质性云云。鄙见已痼。无望其苟同于佗人。而今就盛说而言之。泥沙之水。来谕甚当。水之杂泥。盖可见于水流之后。而其未流之前。所可见者。泂然之本色而已。然水既在于泥沙之中。则自其未流出之时。而已不得离了泥沙而悬空独立。指其泂然者曰本性。指其不离者曰气质性。何不可之有也。朱子论性。何止一二。而皆以不杂不离者。言本性及气质性。未尝有指发后而为言者。此则可按而知也。又况未发之时。气质之性。亦在其中。朱子之训。
舜佐往复。乃至盛谕之谬及耶。大率近世学者。高谈性天。毕竟无补于身心。而只消得閒争竞。此可戒也。况在此时。不必论心说性。更惹外间人讥议也。然屋下合说底话。朱先生之所不禁。则亦不敢有所问而无所答也。舜佐所见明剀。论说精详。吾党中诚不易得。而但其本体合理气之说。恐涉驳杂。四端之谓之理发。固无可疑。而若以七情之理从气出。看作气发。则朱退于此只可曰发于气也。何以曰气之发也。窃念未发之时。理在气上。而事之属乎义理者来感。则此理发而此气随之。所谓四端也。事之属乎形气者来感。则此气发而此理乘之。所谓七情也。看得如此而后。朱退二训。一串可解。而更无苟且捩转之弊矣。且虽如此看得。理之乘气。四七一也。焉有大本上两主之嫌乎。未发前气质性云云。鄙见已痼。无望其苟同于佗人。而今就盛说而言之。泥沙之水。来谕甚当。水之杂泥。盖可见于水流之后。而其未流之前。所可见者。泂然之本色而已。然水既在于泥沙之中。则自其未流出之时。而已不得离了泥沙而悬空独立。指其泂然者曰本性。指其不离者曰气质性。何不可之有也。朱子论性。何止一二。而皆以不杂不离者。言本性及气质性。未尝有指发后而为言者。此则可按而知也。又况未发之时。气质之性。亦在其中。朱子之训。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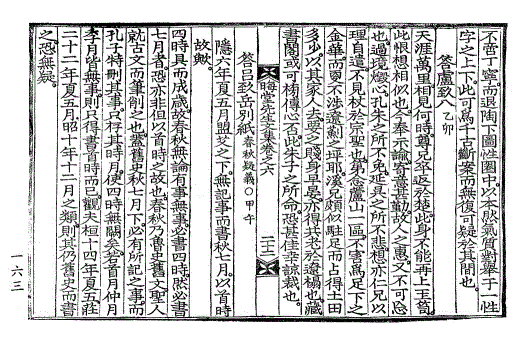 不啻丁宁。而退陶下图性圈中。以本然气质对举于一性字之上下。此可为千古断案而无复可疑于其间也。
不啻丁宁。而退陶下图性圈中。以本然气质对举于一性字之上下。此可为千古断案而无复可疑于其间也。答卢致八(乙卯)
天涯万里。相见何时。尊兄卒返于楚。此身不能再上玉笥。此恨想相似也。今奉示谕。寄意甚勤。故人之惠。又不可忘也。过境燬心。孔朱之所不免。延吴之所不悲。想亦仁兄以理自遣。不见杖于宗圣也。第念芦山一区。不害为足下之金华。而更不涉辽蓟之坪耶。溪兄颇似驻足而占得土田多少。以其家人去。要之贱身早晏。亦得共老于辽榻也。藏书阁或可榜传心否。此朱子之所命。恐甚佳幸谅裁也。
答吕致岳别纸(春秋疑义○甲午)
隐六年夏五月盟艾之下。无记事而书秋七月。以首时故欤。
四时具而成岁。故春秋无论有事无事。必书四时。然必书七月者。恐亦非但以首时之故也。春秋乃鲁史旧文。圣人就古文而笔削之也。盖旧史秋七月下。必有所记之事。而孔子特删其事。只存其时月。使四时无阙矣。若首月仲月季月皆无事。则只得书首时而已。观夫桓十四年夏五,庄二十二年夏五月,昭十年十二月之类。则其仍旧史而书之。恐无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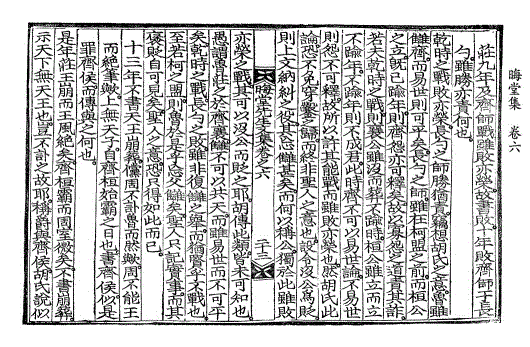 庄九年及齐师战虽败亦荣。故书败。十年败齐师于长勺。虽胜亦责何也。
庄九年及齐师战虽败亦荣。故书败。十年败齐师于长勺。虽胜亦责何也。乾时之战败亦荣。长勺之师胜犹责。窃想胡氏之意。鲁虽雠齐。而易世则可平矣。长勺之师。虽在柯盟之前。而桓公之立。既已踰年。则齐怨亦可释矣。故以寡怨之道责其诈。若夫乾时之战。则襄公虽没而葬不踰时。桓公虽立而立不踰年。不踰年则不成君。此时齐不可以易世论。不易世则怨不可释。故所以许其能战而虽败亦荣也。然胡氏此论。恐不免穿凿之归。而终非圣人之意也。设令没公为贬。则上文纳纠之役。其忘雠甚矣。而何以称公。独于此虽败亦荣之战。其可以没公而贬之耶。胡传此类。皆未可知也。愚谓鲁庄之于齐襄。雠不可以共天。而虽易世而不可平矣。乾时之战。长勺之败。虽非复雠之举。而犹贤乎不战也。至若柯之盟。则鲁于是乎忘父雠矣。圣人只记实事。而其褒贬自可见矣。圣人之意。恐只得如此而已。
十三年不书天王崩葬。傥周不讣鲁而然欤。周不能王而绝笔欤。上无天子。自齐桓始霸之日也。书齐侯。似是罪齐侯。而传与之何也。
是年庄王崩而王风绝矣。齐桓霸而周室微矣。不书崩葬。示天下无天王也。岂不讣之故耶。称爵与齐侯。胡氏说似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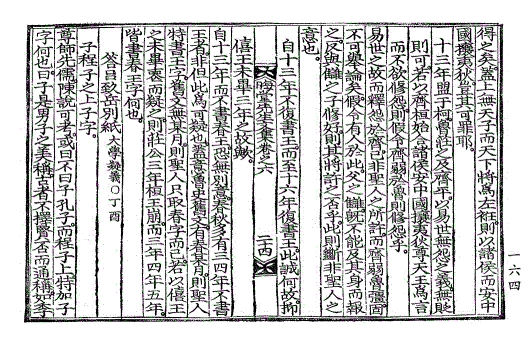 得之矣。盖上无天子而天下将为左衽。则以诸侯而安中国攘夷狄。岂其可罪耶。
得之矣。盖上无天子而天下将为左衽。则以诸侯而安中国攘夷狄。岂其可罪耶。十三年盟于柯。鲁庄之及齐平。以易世无怨之义。无贬则可。若以齐桓始合诸侯安中国攘夷狄尊天王为言而不欲修怨。则假令齐弱于鲁则修怨乎。
易世之故而释怨于齐。已非圣人之所许。而齐弱鲁彊。固不可举论矣。假令有人于此。父之雠。既不能及其身而报之。反与雠之子修好。则其将许之否乎。此则断非圣人之意也。
自十三年不复书王。而至十六年复书王。此诚何故。抑僖王未毕三年之故欤。
自十三年而不书春王。恐无别意。春秋多有三四年不书王者。非但此为可疑也。盖意鲁史旧文。有春某月。则圣人特书王字。旧文无某月。则圣人只取春字而已。若以僖王之未毕丧而疑之。则庄公三年桓王崩。而三年四年五年。皆书春王字何也。
答吕致岳别纸(大学疑义○丁酉)
子程子之上子字。
尊师先儒。陈说可考。或曰不曰子孔子。而程子上。特加子字何也。曰子是男子之美称。古者不择贤否而通称。如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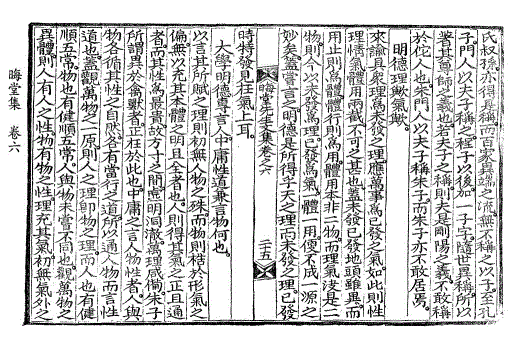 氏叔孙。亦得是称。而百家异端之流。无不称之以子。至孔子。门人以夫子称之。程子以后。加一子字。随世异称。所以著其尊师之义也。若夫子之称。则夫是刚阳之义。不敢称于佗人也。朱门人以夫子称朱子。而朱子亦不敢居焉。
氏叔孙。亦得是称。而百家异端之流。无不称之以子。至孔子。门人以夫子称之。程子以后。加一子字。随世异称。所以著其尊师之义也。若夫子之称。则夫是刚阳之义。不敢称于佗人也。朱门人以夫子称朱子。而朱子亦不敢居焉。明德理欤气欤。
来谕具众理为未发之理。应万事为已发之气。如此则性理情气体用两截。不可之甚也。盖未发已发地头虽异。而用止则为体。体行则为用。体用本非二物。而理气决是二物。则今以未发为理。已发为气。一体一用。便不成一源之妙矣。盖尝言之。明德是所得乎天之理而未发之理。已发时特发见在气上耳。
大学明德专言人。中庸性道兼言物何也。
以言其所赋之理则初无人物之殊。而物则梏于形气之偏。无以充其本体之明且全者也。人则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方寸之间。虚明洞澈。万理咸备。朱子所谓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也。中庸之言人物性者。人与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各有当行之道。所以通人物而言性道也。盖观万物之一原。则人之理即物之理。而人也有健顺五常。物也有健顺五常。人与物未尝不同也。观万物之异体。则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理充其气。初无气外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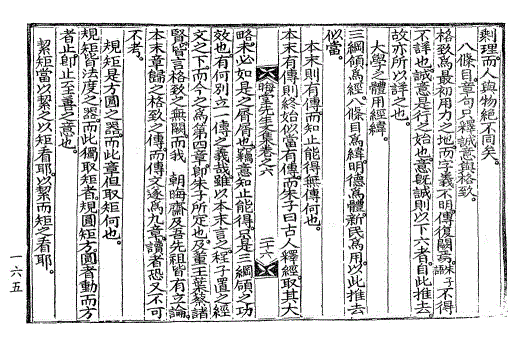 剩理。而人与物绝不同矣。
剩理。而人与物绝不同矣。八条目。章句只释诚意与格致。
格致为最初用力之地。而字义不明。传复阙焉。(朱子语。)不得不详也。诚意是行之始也。意既诚则以下六者。自此推去。故亦所以详之也。
大学之体用经纬。
三纲领为经。八条目为纬。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以此推去似当。
本末则有传。而知止能得无传何也。
本末有传则终始似当有传。而朱子曰古人释经。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窃意知止能得。只是三纲领之功效也。有何别立一传之义哉。虽以本末言之。程子置之经文之下。而今之为第四章。即朱子所定也。及董王叶蔡诸贤。皆言格致之无阙。而我 朝晦斋及吾先祖皆有立论。本末章归之格致之传。而传文遂为九章。读者恐又不可不考。
规矩是方圆之器。而此章但取矩何也。
规矩皆法度之器。而此独取矩者。规圆矩方。圆者动而方者止。即止至善之意也。
絜矩当以絜之以矩看耶。以絜而矩之看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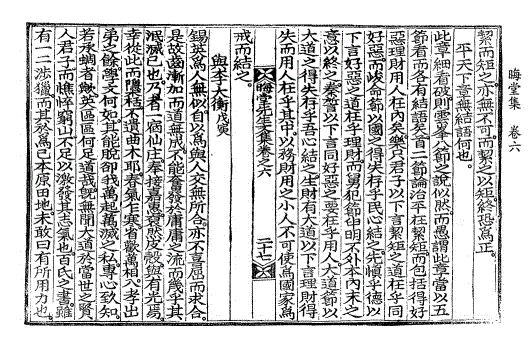 絜而矩之。亦无不可。而絜之以矩。终恐为正。
絜而矩之。亦无不可。而絜之以矩。终恐为正。平天下章无结语何也。
此章细看破。则云峰八节之说似然。而愚谓此章当以五节看而各有结语矣。首二节论治平在絜矩。而包括得好恶理财用人在内矣。乐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乎同好恶。而峻命节以国之得失存乎民心结之。先慎乎德以下言好恶之道在乎理财。而舅犯节申明不外本内末之意以终之。秦誓以下言同好恶之要在乎用人。大道节以大道之得失存乎吾心结之。生财有大道以下言理财得失而用人在乎其中。以务财用之小人不可使为国家为戒而结之。
与李大衡(戊寅)
锡英为人无似。自以为与人交无所合。亦不喜屈而求合。是故齿渐加而道无成。不能奋发于庸庸之流而几乎其泯灭已也。乃者一宿仙庄。奉接嘉惠。裒然皮壳。与有光焉。幸从此而檃栝。不遗曲木耶。春气乍寒。省欢万相。入孝出弟之馀。学文何如。其能脱却我万起万灭之私。专心致知。若承蜩者欤。英区区何足道哉。既无闻大道于当世之贤人君子。而憔悴穷山。不足以激发其志气也。百氏之书。虽有一二涉猎。而其于为己本原田地。未敢曰有所用力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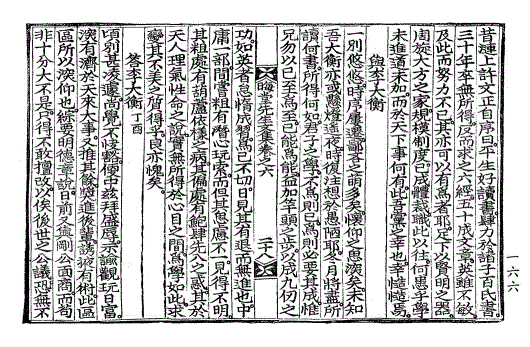 昔涟上许文正自序曰。平生好读书。肆力于诸子百氏书。三十年卒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五十成文章。英虽不敏。及此而努力不已。其亦可以有为者耶。足下以贤明之器。周旋大方之家。规模制度。已成体裁。职此以往。何患乎学未进道未加。而于天下事何有。此吾党之幸也。幸慥慥焉。
昔涟上许文正自序曰。平生好读书。肆力于诸子百氏书。三十年卒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五十成文章。英虽不敏。及此而努力不已。其亦可以有为者耶。足下以贤明之器。周旋大方之家。规模制度。已成体裁。职此以往。何患乎学未进道未加。而于天下事何有。此吾党之幸也。幸慥慥焉。与李大衡
一别悠悠。时序屡迁。鄙吝之萌多矣。怀仰之思深矣。未知吾大衡亦或悬灯遥夜。时复注想于愚陋耶。冬月将尽。所读何书。所得何如。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惟兄勿以已至为至。已能为能。益加竿头之步。以成九仞之功。如英者怠惰成习。为己不切。日见其有退而无进也。中庸一部。间尝粗有潜心玩索。而但其思虑不一。见得不明。其粗处有葫芦依样之病。其偏处有鲍肆先入之惑。其于天人理气性命之说。实无所得于心目之间。为学如此。求变其不美之质得乎。良亦愧矣。
答李大衡(丁酉)
顷别甚凌遽。尚觉不快豁。便中玆拜盛辱。示谕观玩日富。深有济于天来大事。又推其馀。奖进后辈。诱掖有术。此区区所以深仰也。综要明德章说。日前又与刚公面商。而苟非十分大不是。只得不敢擅改。以俟后世之公议。恐无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7H 页
 可。此在诸公从长处之为佳。
可。此在诸公从长处之为佳。与金范初(滢模○乙丑)
一别动经几年。只是无相闻。觉得吾人皆不死于此世也。贤督远来相访。欣然见故人典型而与之相乐也。年老多病。正所相怜。而足下禀质刚介。可幸斯文而久视也。深谷集。吾本生先文也。顷使祚铉替吾致命。丐足下下手。未知曾已寄文以来否。高山讲会时发问。尚无一人答来者。上流风采。若是萧然耶。良可叹息。此间景况。圣启君想以其所目告之。不须道也。
答安华益(丁酉)
堂内营襄。主鬯无人。自多变节。深庸奉悰。第念有庶子而从侄主丧。深恐礼无可据。盖无冢嫡。有妾子父死承后。已是古礼。而嫡妾俱无子然后。告官立后。非大典之制乎。令再从氏无后而亡。以古礼则虽用殷及之例。亦无不可。然东俗庶孽甚贱。绝少承重之例。兄亡有弟。又无移宗之礼。固当取其昭穆。以继再从氏之后。而未立后之前。又遭其父丧。则其庶子安得不主其丧乎。以名则庶子虽贱。以属则子亲而从侄疏。以服则有斩衰小功之异。庶子主丧。容可已乎。况主丧与主祭不同。东西家里尹之所可主者。庶子独不得主之乎。寒冈曰。士大夫之主。固不可委之庶孽。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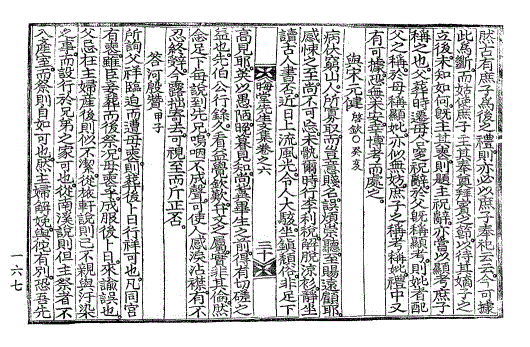 然古有庶子为后之礼。则亦必以庶子奉祀云云。今可据此为断。而姑使庶子主其奉奠拜宾之节。以待其嫡子之立后。未知如何。既主其丧。则题主祝辞。亦当以显考庶子称之也。父葬时迁母合窆祝辞。于父既称显考。则妣者配父之称。于母称显妣。亦似无妨。庶子之称考称妣。礼中又有可据。恐无未安。幸博考而处之。
然古有庶子为后之礼。则亦必以庶子奉祀云云。今可据此为断。而姑使庶子主其奉奠拜宾之节。以待其嫡子之立后。未知如何。既主其丧。则题主祝辞。亦当以显考庶子称之也。父葬时迁母合窆祝辞。于父既称显考。则妣者配父之称。于母称显妣。亦似无妨。庶子之称考称妣。礼中又有可据。恐无未安。幸博考而处之。与宋元健(启钦○癸亥)
病伏穷山。人所寡取。而岂意贱名。误烦崇听。至赐远顾耶。感悚之至。尚不可忘。未骫尔时行李利税。解脱凉衫。静坐读古人书否。近日上流风光。令人大骇。坐镇颓俗。非足下高见耶。英以愚陋。晚暮见知。尚冀毕生之前。得有切磋之益也。先伯公行录。久看益觉钦叹。弁文之属。实非其伦。然念足下每说到先兄。呜咽不成声。可使人感泪沾襟。有不忍终辞。今露拙寄去。可视至而斤正否。
答河殷赞(甲子)
所询父祥临迫而遭母丧。则葬后卜日行祥可也。凡同宫有丧。虽臣妾葬而后祭。况母丧乎。成服后卜日。来谕误也。父忌在主妇产后则似不洁。从旅轩说则己不亲与污染之事。而设行于兄弟之家可也。从南溪说则但主祭者不入产室。而祭则自如可也。然主妇解娩。与佗有别。恐吾先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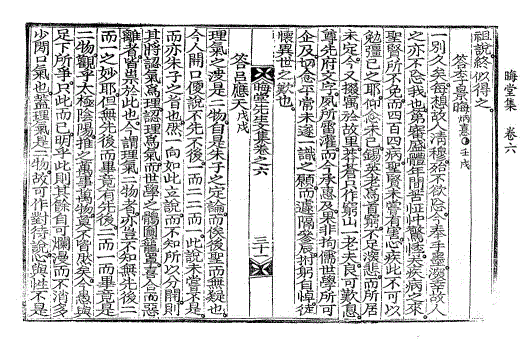 祖说。终似得之。
祖说。终似得之。答李景晦(炳憙○壬戌)
一别久矣。每想故人清穆。殆不欲忘。今奉手墨。深幸故人之亦不忘我也。第审盛体年间苦怔忡惊悸。夫疾病之来。圣贤所不免。而四百四病。圣贤未尝有害。心疾此不可以勉彊已之耶。仰念未已。锡英老为首穷。不足深悲。而所居未定。今又掇寓于故里。莽苍只作穷山一老夫。良可叹息。尊先府文字。夙所雷灌。而今承惠及。果非拘儒世学所可企及。切念平常未遂一识之愿。而遽隔参辰。拊躬自悼。徒怀异世之叹也。
答吕应天(戊戌)
理气之决是二物。自是朱子之定论。而俟后圣而无疑也。今人开口便说不先不后。一而二二而一。此说未尝不是。而亦朱子之旨也。然一向如此立说。而不知所以分开。则其将认气为理。认理为气。而世学之鹘囵笼罩。喜合而恶离者。皆祟于此也。今谓理气二物者。亦岂不知无先后二而一之妙耶。但无先后而毕竟有先后。二而一而毕竟是二物。观乎太极阴阳。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矣。今愚与足下所争。只此而已。明乎此则其馀自可烂漫而不消多少閒口气也。盖理气是二物。故可作对待说。心与性不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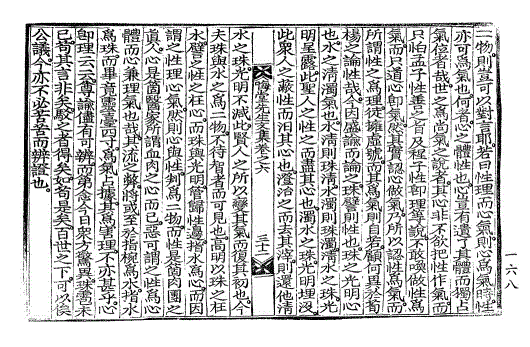 二物。则岂可以对言耶。若曰性理而心气。则心为气时。性亦可为气也。何者。心之体性也。心岂有遗了其体而独占气位者哉。世之为尚气之说者。其心非不欲把性作气。而只怕孟子性善之旨及程子性即理等说。不敢唤做性为气。而只道心即气。然其实认心做气。乃所以认性为气。而所谓性之为理。徒拥虚号。而其为气则自若。顾何异于荀杨之论性哉。今因盛谕而论之。珠譬则性也。珠之光明心也。水之清浊气也。水清则珠清。水浊则珠浊。清水之珠。光明呈露。此圣人之性之而尽其心也。浊水之珠。光明埋没。此众人之蔽性而汩其心也。澄治之而去其滓。则还他清水之珠。光明不减。此贤人之所以变其气而复其初也。今夫珠与水之为二物。不待智者而可见也。高明以珠之在水。譬之性之在心。而珠与光明。管归性边。指水为心。而因谓之性理心气。然则心与性。判为二物。而性是个肉团之真。人心是个医家所谓血肉之心而已。恶可谓之性为心体而心兼理气也哉。其流之弊。将或至于指碗为水。指水为珠。而毕竟灵台四寸。为气占据。其为害理。不亦甚乎。心即理云云。尊谕尽有可辨。而第念今日众方惊异。珠雹未已。苟其言非矣。驳之者得矣。如苟是矣。百世之下。可以俟公议。今亦不必苦苦而辨證也。
二物。则岂可以对言耶。若曰性理而心气。则心为气时。性亦可为气也。何者。心之体性也。心岂有遗了其体而独占气位者哉。世之为尚气之说者。其心非不欲把性作气。而只怕孟子性善之旨及程子性即理等说。不敢唤做性为气。而只道心即气。然其实认心做气。乃所以认性为气。而所谓性之为理。徒拥虚号。而其为气则自若。顾何异于荀杨之论性哉。今因盛谕而论之。珠譬则性也。珠之光明心也。水之清浊气也。水清则珠清。水浊则珠浊。清水之珠。光明呈露。此圣人之性之而尽其心也。浊水之珠。光明埋没。此众人之蔽性而汩其心也。澄治之而去其滓。则还他清水之珠。光明不减。此贤人之所以变其气而复其初也。今夫珠与水之为二物。不待智者而可见也。高明以珠之在水。譬之性之在心。而珠与光明。管归性边。指水为心。而因谓之性理心气。然则心与性。判为二物。而性是个肉团之真。人心是个医家所谓血肉之心而已。恶可谓之性为心体而心兼理气也哉。其流之弊。将或至于指碗为水。指水为珠。而毕竟灵台四寸。为气占据。其为害理。不亦甚乎。心即理云云。尊谕尽有可辨。而第念今日众方惊异。珠雹未已。苟其言非矣。驳之者得矣。如苟是矣。百世之下。可以俟公议。今亦不必苦苦而辨證也。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9H 页
 答吕应天
答吕应天示谕心即理云云。盛谕又如此。只得略陈其曲折。以听足下之去就也。夫心之兼理气。孰可曰不然哉。但心之所以为一身主宰则理也。朱子曰。五脏之心此非心。乃心之舍也。可用药补之。而这个心非菖蒲茯苓之所可补。又曰心不是这一块。则以器言心。便似指宅舍为主翁。又曰心是本气是末。心有知而气无知。又曰理即是心。心即是理。又曰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又曰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又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又曰心固是主宰底。所谓主宰者。即此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据此数说。则朱子之意可知。而今之就兼气处而指理言心者。未必至于大不是也。朱子又尝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世之说性理而心气者。莫不以此为据。然心为太极。著之启蒙。以为象数未形。其理已具之目。而大全答吕子约吴晦叔书。说得心太极之妙。不啻明白。据此则心犹阴阳。未必是正论也。大抵近代心即理之说。乍见而创闻。则若将骇异于世学。然细究之则朱子说。已是十分可据而更无可疑矣。今之论雹此说者。亦皆于朱子说。能一一参考而得其證左耶。来谕曰以不杂而分言则理气心性。俱可对言。愚谓理气则可不杂说。然恐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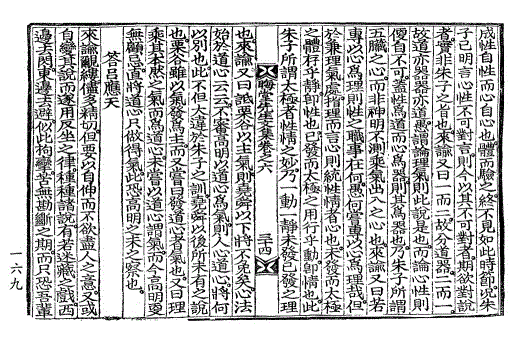 成性自性而心自心也。体而验之。终不见如此时节。况朱子已明言心性不可对言。则今以其不可对者。期欲对说者。实非朱子之旨也。来谕又曰一而二。故分道器。二而一。故道亦器器亦道。愚谓论理气则此说是也。而论心性则便自不可。盖性为道而心为器。则其为器也。乃朱子所谓五脏之心。而非神明不测乘气出入之心也。来谕又曰若专以心为理则性之职事在何。愚何尝专以心为理哉。但于兼理气处。指理而言心则统性情者心也。未发而太极之体存乎静。即性也。已发而太极之用行乎动。即情也。此朱子所谓太极者性情之妙。乃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也。来谕又曰诋栗谷以主气。则尧舜以下将不免矣。心法始于道心云云。不审高明以道心为气。则人心道心。将何以别也。此不但大违于朱子之训。尧舜以后所未有之说也。栗谷虽以气发为主。而又尝曰发道心者气也。又曰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未尝以道心谓气。而今高明更无顾忌。直将道心只做得气。此恐高明之未之察也。
成性自性而心自心也。体而验之。终不见如此时节。况朱子已明言心性不可对言。则今以其不可对者。期欲对说者。实非朱子之旨也。来谕又曰一而二。故分道器。二而一。故道亦器器亦道。愚谓论理气则此说是也。而论心性则便自不可。盖性为道而心为器。则其为器也。乃朱子所谓五脏之心。而非神明不测乘气出入之心也。来谕又曰若专以心为理则性之职事在何。愚何尝专以心为理哉。但于兼理气处。指理而言心则统性情者心也。未发而太极之体存乎静。即性也。已发而太极之用行乎动。即情也。此朱子所谓太极者性情之妙。乃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也。来谕又曰诋栗谷以主气。则尧舜以下将不免矣。心法始于道心云云。不审高明以道心为气。则人心道心。将何以别也。此不但大违于朱子之训。尧舜以后所未有之说也。栗谷虽以气发为主。而又尝曰发道心者气也。又曰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未尝以道心谓气。而今高明更无顾忌。直将道心只做得气。此恐高明之未之察也。答吕应天
来谕覼缕。尽多精切。但要以自伸而不欲尽人之意。又或自变其说而遂用反坐之律。种种诸说。有若迷藏之戏。西边去闪。东边去避。似此拘挛。苦无勘断之期。而只恐吾辈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0H 页
 坐弄光阴。终费了閒说话也。第惟足下于前书中。曰道心原于性命。心果理也。则岂有理以原理云云。此则分明说得道心是气也。指道心而为气。此果尧舜以来所未有之说。而鄙驳恐亦得之矣。今于来谕又曰道心是性。此恐高明自知前说之有误。而弥缝之际。不自知其矫枉而过直耶。道心只看作是性。则其流之弊。将或至于道心体而人心用。此不过张无垢之绪馀而罗困知之糟粕也。今高明抑有契于李文成大本上见得之说耶。高明又谓鄙说分得性与太极而二之。恐亦非鄙之本意也。盖性太极心太极。俱是朱子之训也。愚谓以太极中圈而言则谓性太极亦得。以太极全图而言则谓心太极亦得。但心为太极则所包者甚广。而似亦充足而无馀欠矣。今因盛示。请以心性编排于太极图。盖太极图之中
坐弄光阴。终费了閒说话也。第惟足下于前书中。曰道心原于性命。心果理也。则岂有理以原理云云。此则分明说得道心是气也。指道心而为气。此果尧舜以来所未有之说。而鄙驳恐亦得之矣。今于来谕又曰道心是性。此恐高明自知前说之有误。而弥缝之际。不自知其矫枉而过直耶。道心只看作是性。则其流之弊。将或至于道心体而人心用。此不过张无垢之绪馀而罗困知之糟粕也。今高明抑有契于李文成大本上见得之说耶。高明又谓鄙说分得性与太极而二之。恐亦非鄙之本意也。盖性太极心太极。俱是朱子之训也。愚谓以太极中圈而言则谓性太极亦得。以太极全图而言则谓心太极亦得。但心为太极则所包者甚广。而似亦充足而无馀欠矣。今因盛示。请以心性编排于太极图。盖太极图之中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者。太极之本体也。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者。太极之动而生阳。而阳不是太极之用。即太极之用行乎阳也。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者。太极之静而生阴。而阴不是太极之体。即太极之体立乎阴也。今夫中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即心之本体也。所谓性也。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即心之用。行乎阳也。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即心之体。立乎阴也。行乎阳。即心体之动也。立乎阴。即心体之静也。心之所以为神明不测之妙也。以此推之。心之为太极。不亦明甚乎。体亦心用亦心。体亦太极用亦太极。愚之所以心性不可对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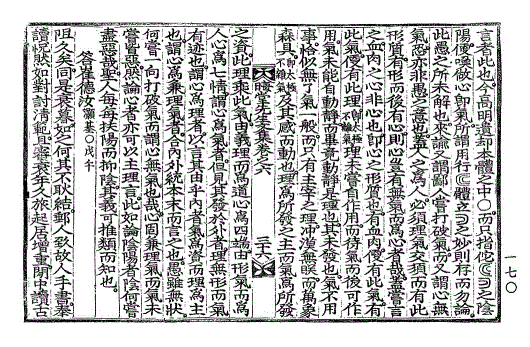 言者此也。今高明遗却本体之中
言者此也。今高明遗却本体之中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而只指佗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之阴阳。便唤做心即气。所谓用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体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GIL 页
之妙则存而勿论。此愚之所未解也。来谕又谓鄙人尝打破气。而又谓心无气。恐亦非愚之意也。盖人之为人。必须理气交须而有此形质。有形而后有心。则心岂有无气而为心者哉。盖尝言之。血肉之心非心也。即心之形质也。有血肉。便有此气。有此气。便有此理。(即太极不离气。)理未尝自作用。而待气而后可作用。气未能自动静。而毕竟动静是理也。其未发也。气不用事。恰似无了气一般。而只有主宰之理。冲漠无眹。而万象森具。(即太极不杂气。)及其感而动也。理为所发之主而气为所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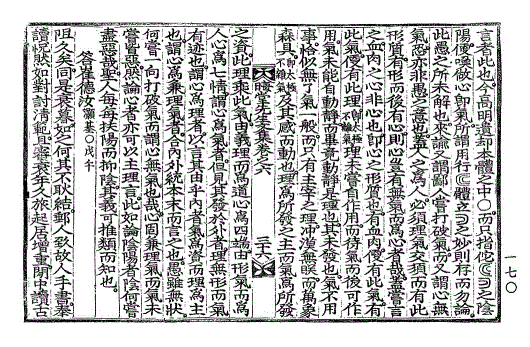 之资。此理乘此气。由义理而为道心为四端。由形气而为人心为七情。谓心为气者。但见其发于外者。理无形而气有迹也。谓心为理者。以言其由乎内者。气为资而理为主也。谓心为兼理气者。合内外统本末而言之也。愚虽无状。何尝一向打破气而谓心无气也哉。心固兼理气而气未尝皆恶。然论心者亦可以主理言。此如论阴阳者阴何尝尽恶哉。圣人每每扶阳而抑阴。其义可推类而知也。
之资。此理乘此气。由义理而为道心为四端。由形气而为人心为七情。谓心为气者。但见其发于外者。理无形而气有迹也。谓心为理者。以言其由乎内者。气为资而理为主也。谓心为兼理气者。合内外统本末而言之也。愚虽无状。何尝一向打破气而谓心无气也哉。心固兼理气而气未尝皆恶。然论心者亦可以主理言。此如论阴阳者阴何尝尽恶哉。圣人每每扶阳而抑阴。其义可推类而知也。答崔德汝(灏基○戊午)
阻久矣。同是衰暮。如之何其不耿结。邮人致故人手书。奉读恍然如对讨清范。且审衰年久旅起居增重。閒中读古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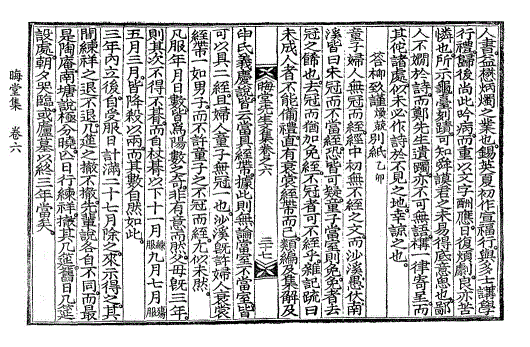 人书。益懋炳烛之业也。锡英夏初作宣福行。与多士讲学行礼。归后尚此吟病。而重以文字酬应。日复烦剧。良亦苦怜也。所示龟台刻迹。可知舜谟君之未易得底意思也。鄙人不娴于诗。而郑先生遗躅。亦不可无语。构一律寄呈。而其佗诸处。似未必作诗于不见之地。幸谅之也。
人书。益懋炳烛之业也。锡英夏初作宣福行。与多士讲学行礼。归后尚此吟病。而重以文字酬应。日复烦剧。良亦苦怜也。所示龟台刻迹。可知舜谟君之未易得底意思也。鄙人不娴于诗。而郑先生遗躅。亦不可无语。构一律寄呈。而其佗诸处。似未必作诗于不见之地。幸谅之也。答柳致谨(焕兢)别纸(乙卯)
童子妇人无冠而绖。经中初无不绖之文。而沙溪,愚伏,南溪皆曰未冠而不当绖。恐皆可疑。童子当室则免。免者去冠之饰也。去冠而犹加免绖。不冠者可不绖乎。杂记疏曰未成人者不能备礼。直有衰裳绖带而已。类编及集解及申氏义庆说。皆云当具绖带。据此则无论当室不当室。皆可以具二绖。且妇人童子无冠一也。沙溪既许妇人衰裳绖带一如男子。而不许童子之不冠而绖。尤似未然。
凡服年月日数。皆为阳数之奇。非有意而然。父母既三年。则其次不得不期。而自杖期以下十一月(练服)九月七月(殇服)五月三月。皆降杀以两。而其数自然如此。
三年内立后。自受服日计满二十七月除之。来示得之。其间练祥之退不退。几筵之撤不撤。先辈说各自不同。而最是陶庵,南塘说极分晓。亡日行练祥。撤其几筵。旧日几筵设处。朝夕哭临。或庐墓以终三年当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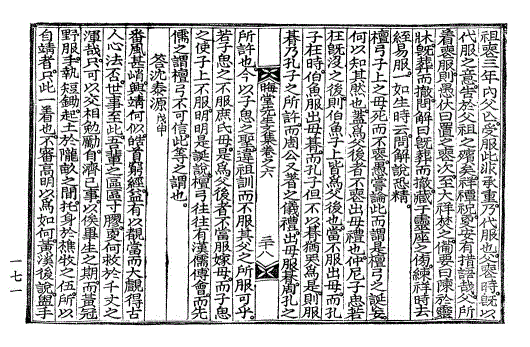 祖丧三年内父亡。受服此非承重。乃代服也。父丧时。既以代服之意。告于父祖之殡矣。祥禫祝。更安有措语哉。父所着丧服。则愚伏曰置之丧次。至大祥焚之。备要曰陈于灵床。既葬而撤。问解曰既葬而撤。藏于灵座之傍。练祥时去绖易服。一如生时云。问解说恐精。
祖丧三年内父亡。受服此非承重。乃代服也。父丧时。既以代服之意。告于父祖之殡矣。祥禫祝。更安有措语哉。父所着丧服。则愚伏曰置之丧次。至大祥焚之。备要曰陈于灵床。既葬而撤。问解曰既葬而撤。藏于灵座之傍。练祥时去绖易服。一如生时云。问解说恐精。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丧。愚尝论此而谓是檀弓之诞妄。何以知其然也。盖为父后者不丧出母礼也。仲尼子思若在既没之后。则伯鱼子上皆为父后也。当不服出母。而孔子在时。伯鱼服出母期。而孔子但不以期犹哭为是。则服期乃孔子之所许。而周公又著之仪礼。出母服期。周孔之所许也。今以子思之圣。违祖训而不服其父之所服可乎。若子思之不服庶氏母。是为父后者不当服嫁母。而子思之使子上不服。明明是诞说。檀弓往往有汉儒傅会。而先儒之谓檀弓不可信。此等之谓也。
答沈泰源(戊申)
番风甚峭。兴靖何似。皓首穷经。益有以睹当而大觑得古人心法否。世事至此。吾辈之区区寸胶。更何救于千丈之浑哉。只可以交相勉励。自济己事。以俟毕生之期。而黄冠野服。手执短锄。起土于陇亩之间。托身于樵牧之伍。所以自靖者。只此一着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黄溪后说。盥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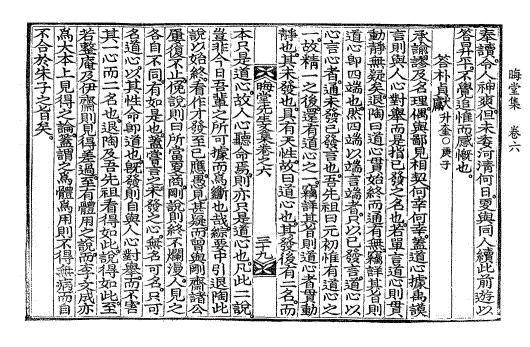 奉读。令人神爽。但未委河清何日。更与同人续此前游以答升平。不觉追惟而感慨也。
奉读。令人神爽。但未委河清何日。更与同人续此前游以答升平。不觉追惟而感慨也。答朴贞献(升奎○庚子)
承谕谬及名理。偶与鄙见相契。何幸何幸。盖道心据禹谟言则与人心对举而是指已发之名也。若单言道心则贯动静无疑矣。退陶曰道心贯始终而通有无。窃详其旨则道心即四端也。然四端以端言端者。只以已发言。道心以心言心者。通未发已发言也。吾先祖曰元初惟有道心之一。故精一之后。还有道心之一。窃详其旨则道心者贯动静也。其未发也。具有天性。故曰道心也。其发后有二名。而本只是道心。故人心听命焉。则亦只是道心也。凡此二说。岂非今日吾辈之所可据而为断也哉。综要中引退陶此说以始终。看作才发至已应。愚见甚疑。而曾与刚斋诸公屡复不止。俛说则曰所当更商。刚说则终不烂漫。人见之各自不同。有如是也。盖尝言之。未发之心。无名可名。只可名道心。以其性命即道也。既发则自与人心对举。而不害其一心而二名也。退陶及吾先祖看得如此。说得如此。至若整庵及伊斋则见得差过。至有体用之说。而李文成亦为大本上见得之论。盖谓之为体为用则不得无病而自不合于朱子之旨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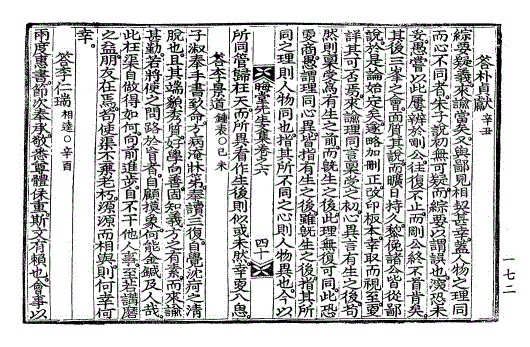 答朴贞献(辛丑)
答朴贞献(辛丑)综要疑义。来谕当矣。又与鄙见相契甚幸。盖人物之理同而心不同者。朱子说初无可疑。而综要以谓误也。深恐未妥。愚尝以此屡辨于刚公。往复不止。而刚公终不首肯矣。其后三峰之会。面质其说。而旷日持久。黎俛诸公皆从鄙说。于是论始定矣。遂略加删正。改印板本。幸取而视至。更详其可否焉。来谕理同言禀受之初。心异言有生之后。苟然则禀受为有生之前。而既生之后。此理无复可同。此恐更商。愚谓理同心异。皆指有生之后。虽既生之后。指其所同之理则人物同也。指其所不同之心则人物异也。今以所同管归在天。而所异看作生后则似或未然。幸更入思。
答李景道(钟表○己未)
子淑奉手书致命。方病淹床笫。奉读三复。自觉沈疴之清脱也。且其端貌秀质。好学向善。固知义方之有素。而来谕甚勤。若将使之问路于盲者。自顾摸象。何能金针及人哉。此在渠自做得如何。向前进步。自不干他人事。至若讲磨之益。朋友在焉。苟使渠不弃老朽。源源而相与。则何幸何幸。
答李仁瑞(相逵○辛酉)
两度惠书。节次奉承。敬悉尊体保重。斯文有赖也。会事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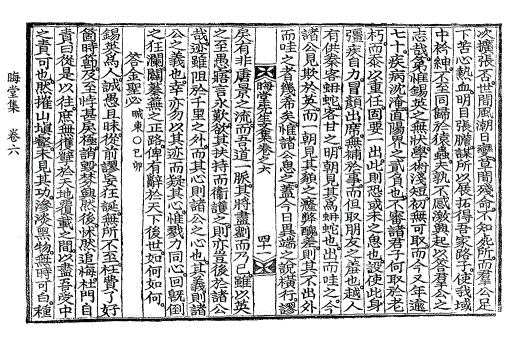 次扩张否。世间风潮日变。草间残命。不知死所。而群公足下苦心热血。明目张胆。谋所以展拓得吾家路子。使我域中衿绅。不至同归于猿虫。夫孰不感激兴起以答群公之志哉。第惟锡英之无状。学术浅短。初无可取。而今又年逾七十。疾病沈淹。直阳界之贰负也。不审诸君子何取于老朽。而忝以重任。固要一出。此则恐或未之思也。设使此身彊疾自力。冒颜出席。无补于事。而但取朋友之羞也。越人有供秦客蚺蛇。客甘之。明朝见其为蚺蛇也。出而哇之。今诸公见欺于英。而一朝见其貌之癃弊丑差。则其不出外而哇之者几希矣。惟诸公思之。盖今日异端之说横行。谬戾有非唐景之流。而吾道一脉。其将尽刘而乃已。虽以英之至愚。寤言永叹。欲其扶持而卫护之。则亦岂后于诸公哉。迹虽阻于千里之外。而其心则诸公之心也。其义则诸公之义也。幸亦勿以其迹而疑其心。惟戮力同心。回既倒之狂澜。辟蓁芜之正路。俾有辞于天下后世。如何如何。
次扩张否。世间风潮日变。草间残命。不知死所。而群公足下苦心热血。明目张胆。谋所以展拓得吾家路子。使我域中衿绅。不至同归于猿虫。夫孰不感激兴起以答群公之志哉。第惟锡英之无状。学术浅短。初无可取。而今又年逾七十。疾病沈淹。直阳界之贰负也。不审诸君子何取于老朽。而忝以重任。固要一出。此则恐或未之思也。设使此身彊疾自力。冒颜出席。无补于事。而但取朋友之羞也。越人有供秦客蚺蛇。客甘之。明朝见其为蚺蛇也。出而哇之。今诸公见欺于英。而一朝见其貌之癃弊丑差。则其不出外而哇之者几希矣。惟诸公思之。盖今日异端之说横行。谬戾有非唐景之流。而吾道一脉。其将尽刘而乃已。虽以英之至愚。寤言永叹。欲其扶持而卫护之。则亦岂后于诸公哉。迹虽阻于千里之外。而其心则诸公之心也。其义则诸公之义也。幸亦勿以其迹而疑其心。惟戮力同心。回既倒之狂澜。辟蓁芜之正路。俾有辞于天下后世。如何如何。答金圣必(晠东○己卯)
锡英为人。诚愚且昧。从前谬妄狂诞。无所不至。枉费了好个时节。及至悖甚戾极。诮毁棼兴然后。怵然追悔。杜门自责曰从是以往。庶无获孽于天地覆载之间。以尽吾受中之责可也。然摧山填壑。未见其功。渗淡黑物。无时可白。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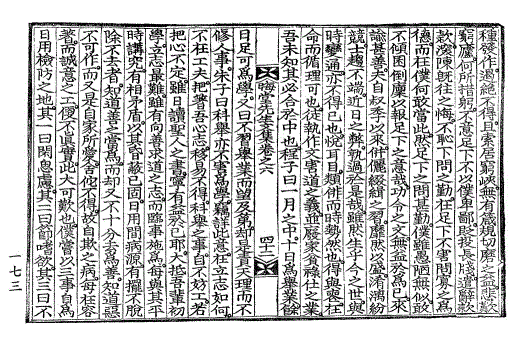 种发作。遏绝不得。且索居穷峡。无有箴规切磨之益。悲叹穷庐。何所措躬。不意足下不以仆卑鄙。贬投长笺。遣辞款款。深陈既往之悔。不耻下问之勤。在足下不害问寡之为德。而在仆何敢当此。然足下之问甚勤。仆虽愚陋无似。敢不倾囷倒廪以报足下之意哉。功令之文。无益于为己。来谕甚善。夫自叔季以来。并俪缀缉之习。靡然以盛。淆漓纷竞。士趋不端。近日之弊。孰过于是哉。虽然生乎今之世。与时变通。亦不得已也。悦耳目。类俳而时势然也。得与丧。在命而循理可也。徒执作文害道之义。并废家贫禄仕之业。吾未知其必合于中也。程子曰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馀日足可为学。又曰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朱子曰科举亦不害为学。窃详此意。在立志如何。不在工夫。把著吾心志。移易不得。科举之事。自不妨工。若把心不定。虽日读圣人之书。宁有益于己耶。大抵吾辈初学。立志最难。虽有向善求道之志。而临事施为。每与其平时讲究。有相矛盾。以其昏蔽已固。日用间病源。有摆不脱除不去者。知道善之当为。而却又不十分去为善。知道恶不可作。而又是自家所爱。舍佗不得。故自欺之病。每在容著。而诚意之工。便不真实。此大可叹也。仆尝以三事自为日用检防之地。其一曰闲思虑。其二曰节嗜欲。其三曰不
种发作。遏绝不得。且索居穷峡。无有箴规切磨之益。悲叹穷庐。何所措躬。不意足下不以仆卑鄙。贬投长笺。遣辞款款。深陈既往之悔。不耻下问之勤。在足下不害问寡之为德。而在仆何敢当此。然足下之问甚勤。仆虽愚陋无似。敢不倾囷倒廪以报足下之意哉。功令之文。无益于为己。来谕甚善。夫自叔季以来。并俪缀缉之习。靡然以盛。淆漓纷竞。士趋不端。近日之弊。孰过于是哉。虽然生乎今之世。与时变通。亦不得已也。悦耳目。类俳而时势然也。得与丧。在命而循理可也。徒执作文害道之义。并废家贫禄仕之业。吾未知其必合于中也。程子曰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馀日足可为学。又曰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朱子曰科举亦不害为学。窃详此意。在立志如何。不在工夫。把著吾心志。移易不得。科举之事。自不妨工。若把心不定。虽日读圣人之书。宁有益于己耶。大抵吾辈初学。立志最难。虽有向善求道之志。而临事施为。每与其平时讲究。有相矛盾。以其昏蔽已固。日用间病源。有摆不脱除不去者。知道善之当为。而却又不十分去为善。知道恶不可作。而又是自家所爱。舍佗不得。故自欺之病。每在容著。而诚意之工。便不真实。此大可叹也。仆尝以三事自为日用检防之地。其一曰闲思虑。其二曰节嗜欲。其三曰不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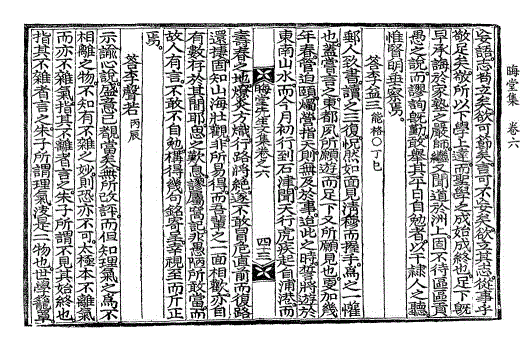 妄语。志苟立矣。欲可节矣。言可不妄矣。欲立其志。从事乎敬足矣。敬所以下学上达。而圣学之成始成终也。足下既早承诲于家塾之严师。继又闻道于洲上。固不待区区贡愚之说。而谬询既勤。敢举其平日自勉者。以干隶人之听。惟贤明垂察焉。
妄语。志苟立矣。欲可节矣。言可不妄矣。欲立其志。从事乎敬足矣。敬所以下学上达。而圣学之成始成终也。足下既早承诲于家塾之严师。继又闻道于洲上。固不待区区贡愚之说。而谬询既勤。敢举其平日自勉者。以干隶人之听。惟贤明垂察焉。答李益三(能格○丁巳)
邮人致书。读之三复。恍然如面见清穆而握手。为之一欢也。盖尝言之。东都夙所愿游。而足下又所愿见也。更加几年春。管迫颐。烛营指天。则无及于事。迨此之时。誓将游于东南山水。而今月初行到石津。闻天行虎疾起自浦港。而寿春之地。燎炎方炽。行路将绝。遂不敢冒危直前而复路还栖。固知山海壮观。非所易得。而吾辈之一面相欢。亦自有数存于其间耶。思之叹息。谬属窝记。非愚陋所敢当。而故人有言。不敢不自勉。构得几句铭寄呈。幸视至而斤正焉。
答李声若(丙辰)
示谕心说。盛意已睹当矣。无所改评。而但知理气之为不相离之物。不知有不杂之妙。则恐亦不可。太极本不离气而亦不杂气。指其不离者言之。朱子所谓不见其始终也。指其不杂者言之。朱子所谓理气决是二物也。世学笼罩。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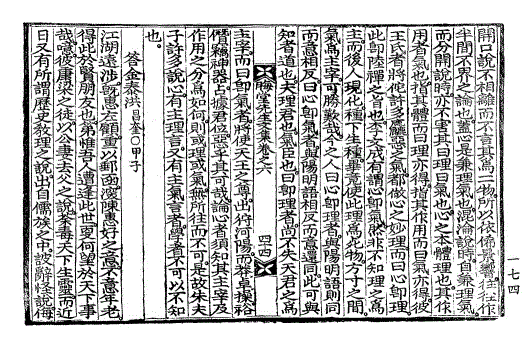 开口说不相离而不言其为二物。所以依俙景响。往往作半间不界之论也。盖心是兼理气也。混沦说时。自兼理气。而分开说时。亦不害其曰理曰气也。心之本体理也。其作用者气也。指其体而曰理亦得。指其作用而曰气亦得。彼王氏者将佗许多粗恶之气。都做心之妙理。而曰心即理。此即陆禅之旨也。李文成有谓心即气。然非不知理之为主。而后人现化。种下生种。毕竟使此理为死物。方寸之间。气为主宰。可胜叹哉。今之人曰心即理者。与阳明语则同而意相反。曰心即气者。与阳明语相反而意还同。此可与知者道也。夫理君也。气臣也。曰即理者。尚不失天君之为主宰。而曰即气者。将使天王之尊。出狩河阳。而莽,卓,操,裕僭窃神器。占据君位。恶乎其可哉。论心者须知其主宰及作用之分为如何。则或理或气。无所往而不可。是故朱夫子许多说心。有主理言。又有主气言者。学者不可以不知也。
开口说不相离而不言其为二物。所以依俙景响。往往作半间不界之论也。盖心是兼理气也。混沦说时。自兼理气。而分开说时。亦不害其曰理曰气也。心之本体理也。其作用者气也。指其体而曰理亦得。指其作用而曰气亦得。彼王氏者将佗许多粗恶之气。都做心之妙理。而曰心即理。此即陆禅之旨也。李文成有谓心即气。然非不知理之为主。而后人现化。种下生种。毕竟使此理为死物。方寸之间。气为主宰。可胜叹哉。今之人曰心即理者。与阳明语则同而意相反。曰心即气者。与阳明语相反而意还同。此可与知者道也。夫理君也。气臣也。曰即理者。尚不失天君之为主宰。而曰即气者。将使天王之尊。出狩河阳。而莽,卓,操,裕僭窃神器。占据君位。恶乎其可哉。论心者须知其主宰及作用之分为如何。则或理或气。无所往而不可。是故朱夫子许多说心。有主理言。又有主气言者。学者不可以不知也。答金泰洪(昌奎○甲子)
江湖远涉。既惠左顾。重以邮函。深陈惠好之意。不意年老。得此于贤朋友也。第惟吾人遭逢此世。更何望于天下事哉。噫。彼康梁之徒。以公妻去父之说。荼毒天下生灵。而近日又有所谓历史教理之说。出自儒族之中。诐辞怪说。侮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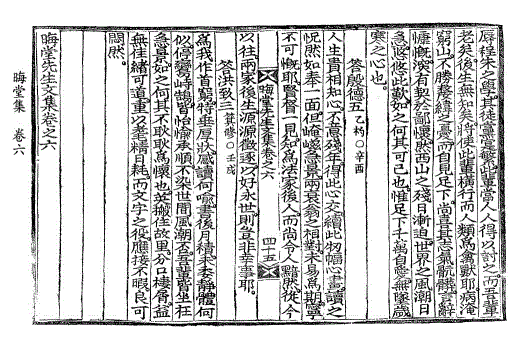 辱程朱之学。其徒党寔繁。此辈当人人得以讨之。而吾辈老矣。后生无知矣。将使此辈横行而人类为禽兽耶。病淹穷山。不胜嫠纬之忧。而自见足下。尚喜其志气肮脏。言辞慷慨。深有契于鄙怀。然西山之残日渐迫。世界之风潮日急。悠悠此叹。如之何其可已也。惟足下千万自爱。无坠岁寒之心也。
辱程朱之学。其徒党寔繁。此辈当人人得以讨之。而吾辈老矣。后生无知矣。将使此辈横行而人类为禽兽耶。病淹穷山。不胜嫠纬之忧。而自见足下。尚喜其志气肮脏。言辞慷慨。深有契于鄙怀。然西山之残日渐迫。世界之风潮日急。悠悠此叹。如之何其可已也。惟足下千万自爱。无坠岁寒之心也。答殷德五(乙杓○辛酉)
人生贵相知心。不意残年。得此心交。续此牣幅心画。读之恍然如奉一面。但崦嵫急景。两衰翁之相对。未易为期。宁不可慨耶。贤督一见。知为法家后人。而尚令人黯然。从今以往。两家后生。源源徵逐。以好永世。则岂非幸事耶。
答洪致三(箕修○壬戌)
为我作首穷。特垂厚状。感读何喻。书后月积。未委静体何似。停鸾峙鹄。皆怡愉承顺。不染世间风潮否。吾辈皆坐在急景。如之何其不耿耿为怀也。英搬住故里。分口栖屑。益无佳绪可道。重以耄精日耗。而文字之役。应接不暇。良可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