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书
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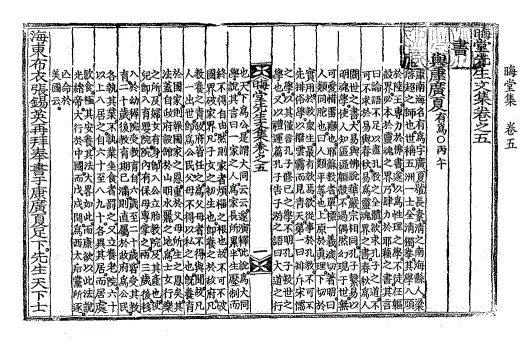 与康广夏(有为○丙午)
与康广夏(有为○丙午)(康南海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清之南海县人。梁启超之师也。世称五洲一士。全清独拳。其学入头于陆王。专力于佛书。遂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必本于灵魂之界。乃肆力于耶苏之书。其言曰论语不足以尽孔教之全体。欲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求于易与春秋。易为灵魂界之书。春秋为人间世之书。大易与佛说华严宗相同。孔子系易以明魂学。使人知区区躯壳。不过偶然幻现于世。无可爱惜留恋也。耶苏教者。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上原于真理。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欲从事于孔教。不可不先排俗学。以拨云雾而见青天。第一曰排斥宋儒之学。以其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也。又以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云云。遂演释此说。为大同学说。其言曰一家之人。为家长所累。半生压制而终不得自由。然则家者烦恼之根也。故不可不破国界破家界。凡子女之初生也。即养之于政府。凡教养之责。政府皆任之。为父母者不得与闻。故凡人一出世。即为公民。父母不得以私之也。既养育于国家。则报国家之恩。重于父母所生之恩矣。其法盖自政府设馆于山明水丽之地。为士女行乐之所。及妇女有身。即入公立胎教院。及其产也。使儿即入育婴院。院内有保母专掌之。两三岁后。移入于幼稚院受教育。自六岁至二十岁。皆受其教育。二十岁后教育期已满。则直属于政府为公民。各执其业。不执业坐食者罚之。又立养老院。六十以上入居之。自六十至八九十。各异其居。而居处饮食。极其安养。其法大略如此。而康欲以此法说光绪帝。大行于中国。而戊戌间。为西太后党所逐。亡命于美国云。)
海东布衣张锡英再拜奉书于康广夏足下。先生天下士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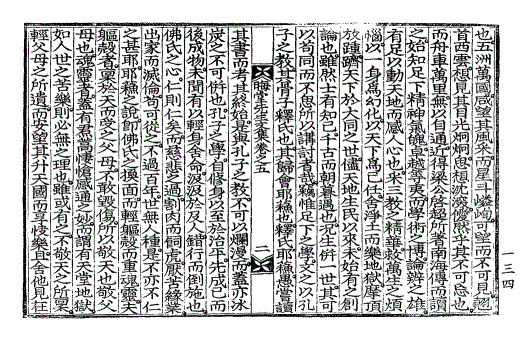 也。五洲万国。咸望其风采。而星斗嶙峋。可望而不可见。翘首西云。想见其目光炯炯。思想沈深。僾然乎其不可忘也。而舟车万里。无以自通。近得梁公启超所著南海传而读之。始知足下精神气魄。卓越等夷。而学术之博。论辨之雄。有足以动天地而感人心也。采三教之精华。救万生之烦恼。以一身为幻化。以天下为己任。舍净土而乐地狱。摩顶放踵。跻天下于大同之世。尽天地生民以来。未始有之创论也。虽然士有知己。千古而朝暮遇也。况生并一世。其可以苟同而不思所以讲讨者哉。窃惟足下之学。文之以孔子之教。其骨子释氏也。其归会耶苏也。释氏,耶苏。愚尝读其书而考其终始。是与孔子之教。不可以烂漫。而盖亦冰炭之不可并也。孔子之学。自修身以至于治平。先成己而后成物。未闻有以轻身舍命。汲汲于及人。错行而倒施也。佛氏之心。仁则仁矣。而慈悲之过。割肉而饲虎。厌苦缘业。出家而灭伦。苟可从之。不过百年。世无人种。是不亦不仁之甚耶。耶苏之说。即佛氏之换面。而轻躯壳而重魂灵。夫躯壳者。禀于天而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敬天也敬父母也。魂灵者。盖有焄蒿悽怆感通之妙。而谓有天堂地狱。如人世之苦乐。则必无之理也。虽或有之。不敬天之所禀。轻父母之所遗。而安望其升天国而享快乐。且舍他见在
也。五洲万国。咸望其风采。而星斗嶙峋。可望而不可见。翘首西云。想见其目光炯炯。思想沈深。僾然乎其不可忘也。而舟车万里。无以自通。近得梁公启超所著南海传而读之。始知足下精神气魄。卓越等夷。而学术之博。论辨之雄。有足以动天地而感人心也。采三教之精华。救万生之烦恼。以一身为幻化。以天下为己任。舍净土而乐地狱。摩顶放踵。跻天下于大同之世。尽天地生民以来。未始有之创论也。虽然士有知己。千古而朝暮遇也。况生并一世。其可以苟同而不思所以讲讨者哉。窃惟足下之学。文之以孔子之教。其骨子释氏也。其归会耶苏也。释氏,耶苏。愚尝读其书而考其终始。是与孔子之教。不可以烂漫。而盖亦冰炭之不可并也。孔子之学。自修身以至于治平。先成己而后成物。未闻有以轻身舍命。汲汲于及人。错行而倒施也。佛氏之心。仁则仁矣。而慈悲之过。割肉而饲虎。厌苦缘业。出家而灭伦。苟可从之。不过百年。世无人种。是不亦不仁之甚耶。耶苏之说。即佛氏之换面。而轻躯壳而重魂灵。夫躯壳者。禀于天而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敬天也敬父母也。魂灵者。盖有焄蒿悽怆感通之妙。而谓有天堂地狱。如人世之苦乐。则必无之理也。虽或有之。不敬天之所禀。轻父母之所遗。而安望其升天国而享快乐。且舍他见在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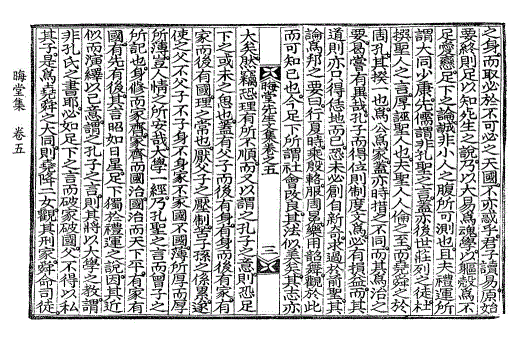 之身。而取必于不可必之天国。不亦惑乎。君子读易。原始要终则足以知死生之说。乃以大易为魂学。以躯壳为不足爱恋。足下之论。诚非小人之腹所可测也。且夫礼运所谓大同少康。先儒谓非孔圣之言。盖亦后世庄列之徒。杜撰圣人之言。厚诬圣人也。夫圣人人伦之至。而尧舜之于周孔。其揆一也。为公为家。盖亦时措之不同。而其为治之要。曷尝有异哉。孔子而得位则制度文为。必有损益。而其道则亦只得恁地而已。恐未必创自新奇。求过于前圣。其论为邦之要曰。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乐用韶舞。观于此而可知已也。今足下所谓社会改良。其法似美矣。其志亦大矣。然窃恐理有所不顺。而又以谓之孔子之意。则恐足下之或未之思也。盖有父子而后有身。有身而后有家。有家而后有国。理之常也。厌父子之压制。苦子孙之系累。遂使之父不父子不子身不身家不家国不国。薄所厚而厚所薄。岂人情之所安哉。大学一经。乃孔圣之言而曾子之所记也。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有家有国。有先有后。其言昭如日星。足下独于礼运之说。因其近似而演绎以己意。谓之孔子之言。则其将以大学之教。谓非孔氏之书耶。必如足下之言而破家破国。父不得以私其子。是为尧舜之大同。则尧降二女。观其刑家。舜命司徒。
之身。而取必于不可必之天国。不亦惑乎。君子读易。原始要终则足以知死生之说。乃以大易为魂学。以躯壳为不足爱恋。足下之论。诚非小人之腹所可测也。且夫礼运所谓大同少康。先儒谓非孔圣之言。盖亦后世庄列之徒。杜撰圣人之言。厚诬圣人也。夫圣人人伦之至。而尧舜之于周孔。其揆一也。为公为家。盖亦时措之不同。而其为治之要。曷尝有异哉。孔子而得位则制度文为。必有损益。而其道则亦只得恁地而已。恐未必创自新奇。求过于前圣。其论为邦之要曰。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乐用韶舞。观于此而可知已也。今足下所谓社会改良。其法似美矣。其志亦大矣。然窃恐理有所不顺。而又以谓之孔子之意。则恐足下之或未之思也。盖有父子而后有身。有身而后有家。有家而后有国。理之常也。厌父子之压制。苦子孙之系累。遂使之父不父子不子身不身家不家国不国。薄所厚而厚所薄。岂人情之所安哉。大学一经。乃孔圣之言而曾子之所记也。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有家有国。有先有后。其言昭如日星。足下独于礼运之说。因其近似而演绎以己意。谓之孔子之言。则其将以大学之教。谓非孔氏之书耶。必如足下之言而破家破国。父不得以私其子。是为尧舜之大同。则尧降二女。观其刑家。舜命司徒。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5L 页
 教以人伦。是不亦参差于盛论耶。呜乎今天下。邪说充斥而圣学化为异端。上下征利而人类丧其本心。此仁人志士之所共叹息也。以足下高明之学。盍思所以挽回尧舜三代之法。使五洲苍生。革心改图。读周孔之书。行周孔之道。顾乃驰心于恍惚不可拟议之地。而不欲盘旋于周孔脚迹之下也。无已则有一焉。请为足下而言之。夫尊卑有序而上下管摄然后。天下不乱而人纪立矣。今世界各国。有国则皆称帝。有人则皆自主。殆非所以顺天地之宜而立人极之道也。天无二日。帝可以二乎。家无二长。人可以各主乎。请足下为文布告天下。使天下各国。极选其国中搢绅儒士之贤。而有识者大会于中原之地。大开眼大开口。讲天下之义理。衡天下之人物。现在世界之中。择其第一等聪明睿知神武不杀之人。推之为天下之主。明春秋大一统之义而万国皆臣属之。自周官制度。历考历代沿革。以至于今世列彊。博采其宜于民国者。立定治制而使万国通行之。因以辨论世界各国之宗教。毋安于旧习。毋阿其所好。大判其是非。若曰孔教是矣。举天下皆主孔教。言孔教者。或理屈辞穷。而释教或耶苏之教是矣。亦可以宗主之矣。其他景教火教路得可兰希腊之属。亦皆十分参订。合于理则取之。非圣叛经。计功利而乱天理者。皆可
教以人伦。是不亦参差于盛论耶。呜乎今天下。邪说充斥而圣学化为异端。上下征利而人类丧其本心。此仁人志士之所共叹息也。以足下高明之学。盍思所以挽回尧舜三代之法。使五洲苍生。革心改图。读周孔之书。行周孔之道。顾乃驰心于恍惚不可拟议之地。而不欲盘旋于周孔脚迹之下也。无已则有一焉。请为足下而言之。夫尊卑有序而上下管摄然后。天下不乱而人纪立矣。今世界各国。有国则皆称帝。有人则皆自主。殆非所以顺天地之宜而立人极之道也。天无二日。帝可以二乎。家无二长。人可以各主乎。请足下为文布告天下。使天下各国。极选其国中搢绅儒士之贤。而有识者大会于中原之地。大开眼大开口。讲天下之义理。衡天下之人物。现在世界之中。择其第一等聪明睿知神武不杀之人。推之为天下之主。明春秋大一统之义而万国皆臣属之。自周官制度。历考历代沿革。以至于今世列彊。博采其宜于民国者。立定治制而使万国通行之。因以辨论世界各国之宗教。毋安于旧习。毋阿其所好。大判其是非。若曰孔教是矣。举天下皆主孔教。言孔教者。或理屈辞穷。而释教或耶苏之教是矣。亦可以宗主之矣。其他景教火教路得可兰希腊之属。亦皆十分参订。合于理则取之。非圣叛经。计功利而乱天理者。皆可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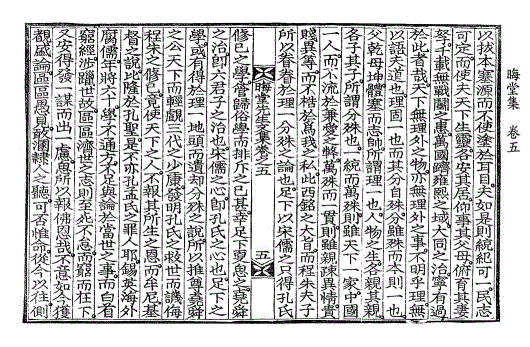 以拔本塞源而不使涂于耳目。夫如是则统纪可一。民志可定。而使夫天下生灵。各安其居。仰事其父母。俯育其妻孥。千载无战斗之患。万国跻雍熙之域。大同之治。宁有过于此者哉。天下无理外之物。亦无理外之事。不明乎理。无以语夫道也。理固一也而其分自殊。分虽殊而本则一也。父乾母坤。体塞而志帅。所谓理一也。人物之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所谓分殊也。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而程朱夫子所以眷眷于理一分殊之论也。足下以宋儒之只得孔氏修己之学。管归俗学而排斥之已甚。幸足下更思之。尧舜之治。即六君子之治也。宋儒之心。即孔氏之心也。足下之学。或有得于理一地头而遗却分殊之说。所以推尊尧舜之公天下而轻觑三代之少康。发明孔氏之救世而讥侮程朱之修己。竟使天下之人。不报其所生之恩。而牟尼,基督之说。比隆于孔圣。是不亦孔孟氏之罪人耶。锡英海外腐儒。年将六十。学不通方。不足与论于当世之事。而白首穷经。涉躐世故。区区济世之志则至死不怠。而穷而在下。又安得发一谋而出一虑。思所以报佛恩哉。不意如今获睹盛论。区区愚见。敢溷隶人之听。可否惟命。从今以往。侧
以拔本塞源而不使涂于耳目。夫如是则统纪可一。民志可定。而使夫天下生灵。各安其居。仰事其父母。俯育其妻孥。千载无战斗之患。万国跻雍熙之域。大同之治。宁有过于此者哉。天下无理外之物。亦无理外之事。不明乎理。无以语夫道也。理固一也而其分自殊。分虽殊而本则一也。父乾母坤。体塞而志帅。所谓理一也。人物之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所谓分殊也。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而程朱夫子所以眷眷于理一分殊之论也。足下以宋儒之只得孔氏修己之学。管归俗学而排斥之已甚。幸足下更思之。尧舜之治。即六君子之治也。宋儒之心。即孔氏之心也。足下之学。或有得于理一地头而遗却分殊之说。所以推尊尧舜之公天下而轻觑三代之少康。发明孔氏之救世而讥侮程朱之修己。竟使天下之人。不报其所生之恩。而牟尼,基督之说。比隆于孔圣。是不亦孔孟氏之罪人耶。锡英海外腐儒。年将六十。学不通方。不足与论于当世之事。而白首穷经。涉躐世故。区区济世之志则至死不怠。而穷而在下。又安得发一谋而出一虑。思所以报佛恩哉。不意如今获睹盛论。区区愚见。敢溷隶人之听。可否惟命。从今以往。侧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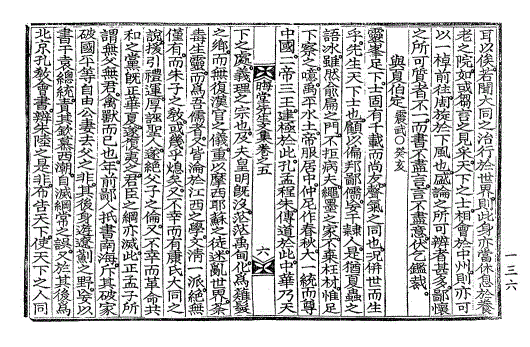 耳以俟。若闻大同之治行于世界。则此身亦当休息于养老之院。如或刍言之见采。天下之士。相会于中州。则亦可以一棹前往。周旋于下风也。盛论之所可辨者甚多。鄙怀之所可质者不一。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伏乞鉴裁。
耳以俟。若闻大同之治行于世界。则此身亦当休息于养老之院。如或刍言之见采。天下之士。相会于中州。则亦可以一棹前往。周旋于下风也。盛论之所可辨者甚多。鄙怀之所可质者不一。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伏乞鉴裁。与夏伯定(震武○癸亥)
灵峰足下。士固有千载而尚友。声气之同也。况并世而生乎。先生天下士也。顾以偏邦鄙儒。妄干隶人。是犹夏虫之语冰。虽然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家。不弃枉材。惟足下察之。噫。禹平水土。帝服居中。仲尼作春秋。大一统而尊中国。二帝三王。建极于此。孔孟程朱。传道于此。中华乃天下之处。义理之宗也。及夫皇明既没。茫茫禹甸。化为薙发之乡。而无复汉官之仪。重以摩西耶苏之徒。迷乱世界。荼毒生灵。而为吾儒者。又皆沦于江西之学。文清一派。绝无仅有。而朱子之教。或几乎熄矣。又不幸而有康氏大同之说。援引礼运。厚诬圣人。遂绝父子之伦。又不幸而革命共和之党既正华夏。遂复夷之。君臣之纲亦灭。此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禽兽而已也。年前鄙人抵书南海。斥其破家破国平等自由公妻去父之非。其后身游辽蓟之野。妄以书干袁总统。责其钦慕西潮。自灭纲常之误。又于其后为北京孔教会书。辨朱陆之是非。布告天下。使天下之人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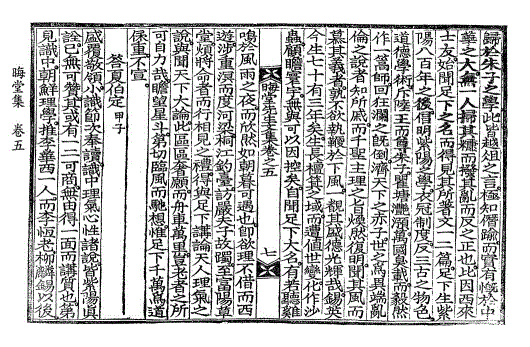 归于朱子之学。此皆越俎之言。极知僭踰。而实有慨于中华之大。无一人扫其糠而拨其乱而反之正也。比因西来士友。始闻足下之名而得见其所著文一二篇。足下生紫阳八百年之后。倡明紫阳之学。衣冠制度。反三古之物色。道德学术。斥陆王而尊朱子。瞿塘滟滪。万国臭载。而毅然作一篙师。回狂澜之既倒。济天下之赤子。世之为异端乱伦之说者知所戚。而千圣主理之旨焕然复明。闻其风而慕其义者。孰不欲执鞭于下风。一睹其盛德光辉哉。锡英今生七十有三年矣。生长檀箕之域。而遭值世变。化作沙虫。顾瞻寰宇。无与可以因控矣。自闻足下大名。有若听鸡鸣于风雨之夜。而欣然如朝暮可遇也。即欲理不借而西游。涉重溟而度河梁。桐江钓台。访严夫子故躅。至富阳草堂。烦将命者而行相见之礼。得与足下讲论天人理气之说。与闻天下大论。此区区奢愿。而舟车万里。岂老者之所可自力哉。瞻望星斗。第切临风而驰想。惟足下千万为道保重。不宣。
归于朱子之学。此皆越俎之言。极知僭踰。而实有慨于中华之大。无一人扫其糠而拨其乱而反之正也。比因西来士友。始闻足下之名而得见其所著文一二篇。足下生紫阳八百年之后。倡明紫阳之学。衣冠制度。反三古之物色。道德学术。斥陆王而尊朱子。瞿塘滟滪。万国臭载。而毅然作一篙师。回狂澜之既倒。济天下之赤子。世之为异端乱伦之说者知所戚。而千圣主理之旨焕然复明。闻其风而慕其义者。孰不欲执鞭于下风。一睹其盛德光辉哉。锡英今生七十有三年矣。生长檀箕之域。而遭值世变。化作沙虫。顾瞻寰宇。无与可以因控矣。自闻足下大名。有若听鸡鸣于风雨之夜。而欣然如朝暮可遇也。即欲理不借而西游。涉重溟而度河梁。桐江钓台。访严夫子故躅。至富阳草堂。烦将命者而行相见之礼。得与足下讲论天人理气之说。与闻天下大论。此区区奢愿。而舟车万里。岂老者之所可自力哉。瞻望星斗。第切临风而驰想。惟足下千万为道保重。不宣。答夏伯定(甲子)
盛覆敬领。小识节次奉读。识中理气心性诸说。皆紫阳真诠。已无可赞。其或有一二可商。无由得一面而讲质也。第见识中。朝鲜理学。推李华西一人。而李恒老,柳麟锡以后。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7L 页
 知有程朱之学。此恐传闻之误也。敝邦虽僻在海隅。而箕圣传八条之教。在高丽末。郑圃隐梦周始倡理学。逮夫我朝。最盛于李退溪滉。而若前若后。名贤辈出。洛闽之学。焕然大明。夫自满清以来。天下晦盲。而敝邦称小中华。非天下人之公评乎。李华西,柳毅庵。皆近年人。今曰李柳以后知有程朱则不词也。小识一出。将使世界公传。其可使有一字差爽乎。身为东人。不敢不告知于门下诸子。不罪不罪。
知有程朱之学。此恐传闻之误也。敝邦虽僻在海隅。而箕圣传八条之教。在高丽末。郑圃隐梦周始倡理学。逮夫我朝。最盛于李退溪滉。而若前若后。名贤辈出。洛闽之学。焕然大明。夫自满清以来。天下晦盲。而敝邦称小中华。非天下人之公评乎。李华西,柳毅庵。皆近年人。今曰李柳以后知有程朱则不词也。小识一出。将使世界公传。其可使有一字差爽乎。身为东人。不敢不告知于门下诸子。不罪不罪。与李南彬(文治○甲寅)
锡英窃伏穷荒。无复望于天下之事。而区区一念。时有往来于中州山水。思与贤士大夫讲道论理。以正其平生所学。而不但蹩躠之没勇。且怕中华之风气不古。大市平天。无以见怜于诸君子矣。不自意大人先生降屈尊威。远赐枉临。半日谈讨。窃观文章赡富。义理精剀。可知其学术之正知见之博。信如将命者之所传矣。噫。陆禅之说。怀襄于天下。而既又天主耶苏之学。靡烂生灵。流毒寰宇。凡我孔氏之徒。无地可归。此岂但唐景之流哉。洪水猛兽。不足喻其为祸也。窃念大兄求齐于庄岳之间。思所以绍述圣学。糠秕世教而百川倒澜。非只手之可障。东出辽阳。得韩溪翁而友之。遂复远涉江湖。声光乃及于敝庐。此固声气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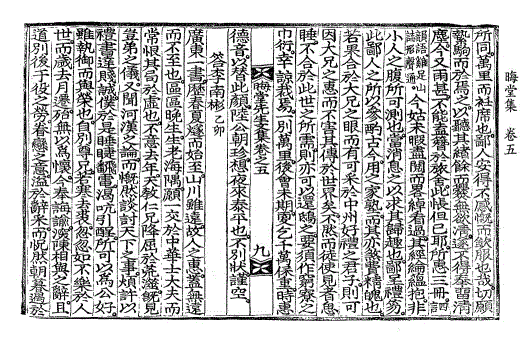 所同。万里而衽席也。鄙人安得不感慨而钦服也哉。切愿絷驹而于焉之。以听其绪馀而爨无欲凊。遂不得奉留清尘。今又雨甚。不能盍簪于旅舍。此怅但已耶。所惠三册。(四言韵语,鸡足山志形声通。)今姑未暇尽阅而略绰看过。其经纶蕴抱。非小人之腹所可测也。当消息之以求其归趣也。鄙呈礼笏。此鄙人之所以参酌古今。用之家塾。而其亦煞费精魄也。若果合于大兄之眼而有可采于中州好礼之君子。则可因大兄之惠而不害其传于世界矣。不然而徒使见者思睡。不合于此世之所需。则亦可以还鸱之。要须作穷寮之巾衍。幸谅裁焉。一别万里。后会未期。更乞千万保重。时惠德音。以替此颜。陆公朝珍。想夜来泰平也。不别状。谨空。
所同。万里而衽席也。鄙人安得不感慨而钦服也哉。切愿絷驹而于焉之。以听其绪馀而爨无欲凊。遂不得奉留清尘。今又雨甚。不能盍簪于旅舍。此怅但已耶。所惠三册。(四言韵语,鸡足山志形声通。)今姑未暇尽阅而略绰看过。其经纶蕴抱。非小人之腹所可测也。当消息之以求其归趣也。鄙呈礼笏。此鄙人之所以参酌古今。用之家塾。而其亦煞费精魄也。若果合于大兄之眼而有可采于中州好礼之君子。则可因大兄之惠而不害其传于世界矣。不然而徒使见者思睡。不合于此世之所需。则亦可以还鸱之。要须作穷寮之巾衍。幸谅裁焉。一别万里。后会未期。更乞千万保重。时惠德音。以替此颜。陆公朝珍。想夜来泰平也。不别状。谨空。答李南彬(乙卯)
广东一书。历春夏燧而始至。山川虽远。故人之惠。盖无远而不至也。区区晚生。生老海隅。愿一交于中华士大夫而常恨其局于虚也。不意去年。天教仁兄降屈于荒澨。既见岂弟之仪。又闻河汉之论。而慨然谈讨天下之事。烦许以礼书达贱诚。仆于是睡睫翻电。渴吭引酲。所可以为公好。虽执御而与荣也。自别尊兄。若寒去裘。忽忽如不乐于人世。而岁去月迁。殆无以为怀。今奉诲谕。深陈相与之辞。且道别后于役之劳。眷恋之意。溢于辞采。而恍然朝暮遇于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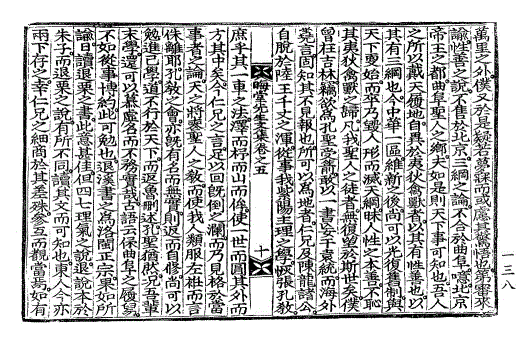 万里之外。仆又于是疑若梦寐而或虑其惊悟也。第审来谕。性善之说。不售于北京。三纲之论。不合于曲阜。噫。北京帝王之都。曲阜圣人之乡。夫如是则天下事可知也。吾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自异于夷狄禽兽者。以其有性善也。以其有三纲也。今中华一区。维新之后。尚可以光复旧制。与天下更始。而卒乃毁人形而灭天纲。昧人性之本善。不耻其夷狄禽兽之归。凡我圣人之徒者。无复望于斯世矣。仆曾在吉林。窃欲为孔圣受箭。敢以一书妄干袁统。而海外荛言。固知其不见报也。所可以为地者。仁兄及陈龙诸公。自脱于陆王千丈之浑。从事我紫阳主理之学。恢张孔教。庶乎其一车之法。泽而杼而山而侔。使一世而圆其外而方其中矣。今仁兄之言。足以回既倒之澜。而乃见格于当事者之论。天之将丧圣人之教。而使我人类服左衽而言侏离耶。孔教之会。亦既有名而无实。则返而自修。尚可以勉进己学。道不行于天下。而返鲁删述。孔圣犹然。况吾辈末学。还可以慕虚名而不务实哉。古语云保曲阜之履舄。不如从事博约。此可勉也。退溪书之为洛闽正宗。果如所谕。日读退栗之书。此意甚佳。但四七理气之说。退说本于朱子。而退栗之说。有所不同。读其文而可知也。东人今亦两下存之。幸仁兄之细商于其差殊。参互而睹当焉。如有
万里之外。仆又于是疑若梦寐而或虑其惊悟也。第审来谕。性善之说。不售于北京。三纲之论。不合于曲阜。噫。北京帝王之都。曲阜圣人之乡。夫如是则天下事可知也。吾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自异于夷狄禽兽者。以其有性善也。以其有三纲也。今中华一区。维新之后。尚可以光复旧制。与天下更始。而卒乃毁人形而灭天纲。昧人性之本善。不耻其夷狄禽兽之归。凡我圣人之徒者。无复望于斯世矣。仆曾在吉林。窃欲为孔圣受箭。敢以一书妄干袁统。而海外荛言。固知其不见报也。所可以为地者。仁兄及陈龙诸公。自脱于陆王千丈之浑。从事我紫阳主理之学。恢张孔教。庶乎其一车之法。泽而杼而山而侔。使一世而圆其外而方其中矣。今仁兄之言。足以回既倒之澜。而乃见格于当事者之论。天之将丧圣人之教。而使我人类服左衽而言侏离耶。孔教之会。亦既有名而无实。则返而自修。尚可以勉进己学。道不行于天下。而返鲁删述。孔圣犹然。况吾辈末学。还可以慕虚名而不务实哉。古语云保曲阜之履舄。不如从事博约。此可勉也。退溪书之为洛闽正宗。果如所谕。日读退栗之书。此意甚佳。但四七理气之说。退说本于朱子。而退栗之说。有所不同。读其文而可知也。东人今亦两下存之。幸仁兄之细商于其差殊。参互而睹当焉。如有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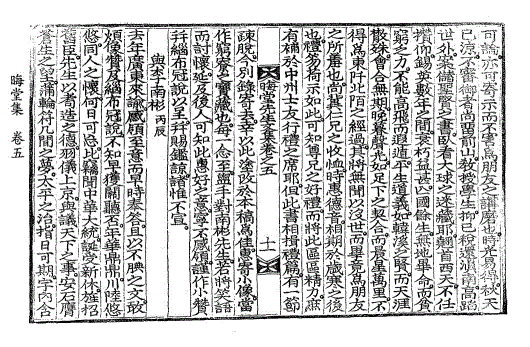 可论。亦可寄示而不害为朋友之讲磨也。时光易得。秋天已凉。不审御者尚留前山。教授学生。抑已税还滇南。高蹈世外。案储圣贤之书。卧看大球之迷藏耶。翘首西天。不任攒仰。锡英数年之间。衰朽益甚。亡国馀生。无地毕命。而贫穷乏力。不能高飞而遐遁。平生道义。如韩溪之贤。而天涯散殊。会合无期。晚暮声光。如足下之契合。而晨星万里。不得为东阡北陌之经过。其将无闻以没世。而毕竟为朋友之所羞也。尚冀仁兄之收恤。时惠德音。相期于岁寒之后也。礼笏荷示如此。可知尊兄之好礼。而将此区区精力。庶有补于中州士友行礼之席耶。但此书相揖礼篇。有一节疏脱。今别录寄去。幸以此涂改于本稿为佳。惠寄小像。当作穷寮之宝藏也。每一念至。盥手对南彬先生。若将笑语而讨怀。延及后人。可知此惠好之意。宁不感领。谨作小赞并缁布冠说以呈。并赐鉴谅。诸惟不宣。
可论。亦可寄示而不害为朋友之讲磨也。时光易得。秋天已凉。不审御者尚留前山。教授学生。抑已税还滇南。高蹈世外。案储圣贤之书。卧看大球之迷藏耶。翘首西天。不任攒仰。锡英数年之间。衰朽益甚。亡国馀生。无地毕命。而贫穷乏力。不能高飞而遐遁。平生道义。如韩溪之贤。而天涯散殊。会合无期。晚暮声光。如足下之契合。而晨星万里。不得为东阡北陌之经过。其将无闻以没世。而毕竟为朋友之所羞也。尚冀仁兄之收恤。时惠德音。相期于岁寒之后也。礼笏荷示如此。可知尊兄之好礼。而将此区区精力。庶有补于中州士友行礼之席耶。但此书相揖礼篇。有一节疏脱。今别录寄去。幸以此涂改于本稿为佳。惠寄小像。当作穷寮之宝藏也。每一念至。盥手对南彬先生。若将笑语而讨怀。延及后人。可知此惠好之意。宁不感领。谨作小赞并缁布冠说以呈。并赐鉴谅。诸惟不宣。与李南彬(丙辰)
去年广东来谕。感领至意而早时奉答。且以不腆之文。敢烦像赞及缁布冠说。不知早获关听否。年华鼎鼎。川陆悠悠。同人之怀。何日可忘。比窃闻中华大统。诞受新休。旌招旧臣。先生以耇造之德。羽仪上京。与议天下之事。安石膺苍生之望。蒲轮符几间之梦。太平之治。指日可期。宇内含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9L 页
 生。夫孰不延颈以望哉。顾惟海外残命。无所依归。所愿望者。惟在中华。而匏系一方。不得蒙至治之泽。虚生一世。不得与中华士大夫并列于有为之时。以伸其有为之志。纵不欲歌白水而自售。安得无拊凌云而自惜哉。窃念天下大势。已大定于共和。此盖气数之使然。非人力之问何也。然论共和者。每以圣贤之学为腐败没用。此则不词。虽使山河大地。都陷于气机之中。周公之礼。孔子之教。便不可一日休罢。治天下而苟不以周公孔子。其将做人类不得。虽欲为共和之治。宁可得乎。大兄于此。盖亦良遂而总知。今居庙堂之上。与闻国政。平生所学。正宜今日用得。勉自修敕。以幸天下后世。此区区之望也。
生。夫孰不延颈以望哉。顾惟海外残命。无所依归。所愿望者。惟在中华。而匏系一方。不得蒙至治之泽。虚生一世。不得与中华士大夫并列于有为之时。以伸其有为之志。纵不欲歌白水而自售。安得无拊凌云而自惜哉。窃念天下大势。已大定于共和。此盖气数之使然。非人力之问何也。然论共和者。每以圣贤之学为腐败没用。此则不词。虽使山河大地。都陷于气机之中。周公之礼。孔子之教。便不可一日休罢。治天下而苟不以周公孔子。其将做人类不得。虽欲为共和之治。宁可得乎。大兄于此。盖亦良遂而总知。今居庙堂之上。与闻国政。平生所学。正宜今日用得。勉自修敕。以幸天下后世。此区区之望也。与李南彬(乙丑)
南彬足下。榆晖冉冉。吾辈馀生几何。不相闻至此耶。清标盛德。每不能忘于怀。而所不能一字书者。不知其所住何地。但足下之于贱身。不亦计较而甚忘耶。第惟中州近日风涛益险。而未闻足下之贤。得志于岩廊之上。天下事又可知。无由得对此衰颜。说得全球风景。握手而一欷也。北京孔教。比益扩张否。世事至此。此一着。不可不明目而张胆。幸自勉旃。仆所著礼笏。布示同志。而或有补于行礼之节否。此笏及仪礼集传。俱被少辈刊行。而年前邮付一帙。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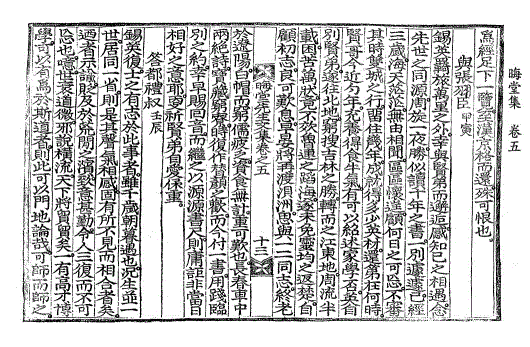 为经足下一览。至汉京格而还。殊可恨也。
为经足下一览。至汉京格而还。殊可恨也。与张羽臣(甲寅)
锡英羁旅万里之外。幸与贤弟而邂逅。感知己之相遇。念先世之同源。周旋一夜。胜似读十年之书。一别遽遽。已经三岁。海天茫茫。无由相闻。区区怀𨓏。顾何日之可忘。不审其时双城之行。留住几年。成就得多少英材。还第在何时。贤哥今近勺年。充养得食牛气。有可以绍述家学否。英自别贤弟。遂往北地。穷搜吉林之胜。转而之江东地。周流半载。困苦万状。竟不效鲁连之蹈海。遂未免灵均之返楚。自顾初志。良可叹息。早晏将再渡浿洲。思与一二同志。终老于辽阳。白帽而穷儒疲乏。资食无计。重可叹也。长春车中两绝诗。宝藏穷寮。时复作替颜之欢。而今付一书。用践临别之约。幸早赐回音。而继之以源源书尺。则庸讵非当日相好之意耶。更祈贤弟自爱保重。
答都礼叔(壬辰)
锡英复。士之有志于此事者。虽千岁朝暮遇也。况生并一世。居同一省。则是其声气相感。固有所不见而相合者矣。乃者示谕。贬及于荒閒之滨。致意甚勤。令人三复而不可忘也。噫。世衰道微。邪说横流。天下将贸贸矣。一有高才博学。可以有为于斯道者。则此可以门地论哉。可师而师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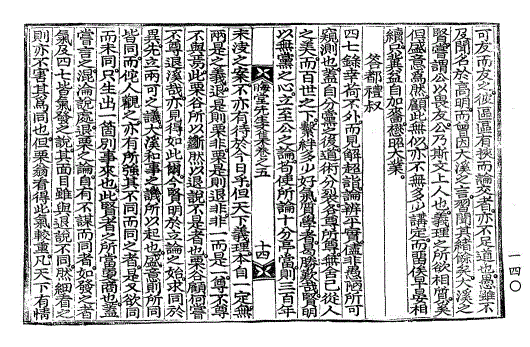 可友而友之。彼区区有挟而论交者。亦不足道也。愚虽不及闻名于高明。而曾因大溪之言。习闻其绪馀矣。大溪之贤。尝谓公以畏友。公乃斯文上人也。义理之所欲相质。奚但盛意为然。顾此无似。亦不无多少讲定。而留俟早晏相续。只冀益自加啬。懋昭大业。
可友而友之。彼区区有挟而论交者。亦不足道也。愚虽不及闻名于高明。而曾因大溪之言。习闻其绪馀矣。大溪之贤。尝谓公以畏友。公乃斯文上人也。义理之所欲相质。奚但盛意为然。顾此无似。亦不无多少讲定。而留俟早晏相续。只冀益自加啬。懋昭大业。答都礼叔
四七录幸荷不外。而见解超诣。论辨平实。尽非愚陋所可窥测也。盖自分党之后。道术分裂。各尊所尊。无舍己从人之美。而百世之下。系绊多少好气质学者。曷胜叹哉。贤明以无党之心。立至公之论。苟使所论十分亭当。则三百年未决之案。不亦有待于今日乎。但天下义理。本自一定。无两是之义。退是则栗非。栗是则退非。非一而是一。尊不尊不与焉。此栗谷所以断然以退说不是者也。栗谷顾何尝不尊退溪哉。亦见得如此尔。今贤明于立论之始。求同于异。先立两可之议。大溪和事之讥所以起也。盛意则所同皆同。而佗人观之。亦有所强其不同而同之者。是又欲同而未同。只生出一个别事来也。此贤者之所当更商也。盖尝言之。混沦说处。退栗之论。自有不谋而同者。如发之者气及四七皆气发之说。其面目虽与退说不同。然细看之则亦不害其为同也。但栗翁看得此气较重。凡天下有情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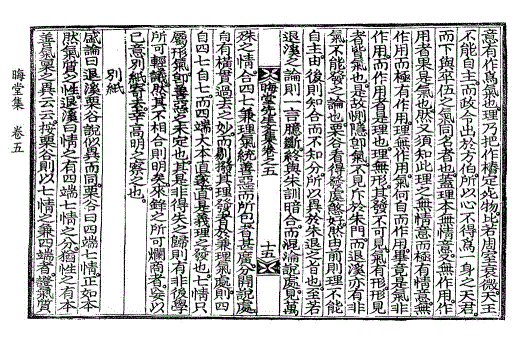 意有作为气也。理乃把作桩定死物。比若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主。而政令出于方伯。所以心不得为一身之天君。而下与卒伍之气同名者也。盖理本无情意。又无作用。作用者果是气也。然又须知此理之无情意而极有情意。无作用而极有作用。理无作用。气何自而作用。毕竟是气非作用。而作用者是理也。理无形。其发不可见。气有形。形见者皆气也。是故恻隐即气。不见斥于朱门。而退溪亦有非气不能发之论也。栗谷看得发处煞好。然由前则理不能自主。由后则知合而不知分。所以异于朱退之旨也。至若退溪之论则一言臆断。终与朱训暗合。而混沦说处。见万殊之情。合四七兼理气统善恶而所包者甚广。分开说处。自有横贯过去之妙。而剔拨其理发者于兼理气处。则四自四七自七。而四端大本直遂。直是义理之发也。七情只属形气。即善恶之未定也。其是非得失之归则有非后学所可轻议。然其不相合则明矣。来录之所可烂商者。妄以己意别纸寄去。幸高明之察之也。
意有作为气也。理乃把作桩定死物。比若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主。而政令出于方伯。所以心不得为一身之天君。而下与卒伍之气同名者也。盖理本无情意。又无作用。作用者果是气也。然又须知此理之无情意而极有情意。无作用而极有作用。理无作用。气何自而作用。毕竟是气非作用。而作用者是理也。理无形。其发不可见。气有形。形见者皆气也。是故恻隐即气。不见斥于朱门。而退溪亦有非气不能发之论也。栗谷看得发处煞好。然由前则理不能自主。由后则知合而不知分。所以异于朱退之旨也。至若退溪之论则一言臆断。终与朱训暗合。而混沦说处。见万殊之情。合四七兼理气统善恶而所包者甚广。分开说处。自有横贯过去之妙。而剔拨其理发者于兼理气处。则四自四七自七。而四端大本直遂。直是义理之发也。七情只属形气。即善恶之未定也。其是非得失之归则有非后学所可轻议。然其不相合则明矣。来录之所可烂商者。妄以己意别纸寄去。幸高明之察之也。别纸
盛论曰退溪栗谷说似异而同。栗谷曰四端七情。正如本然气质之性。退溪曰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善气禀之异云云。按栗谷则以七情之兼四端者。證气质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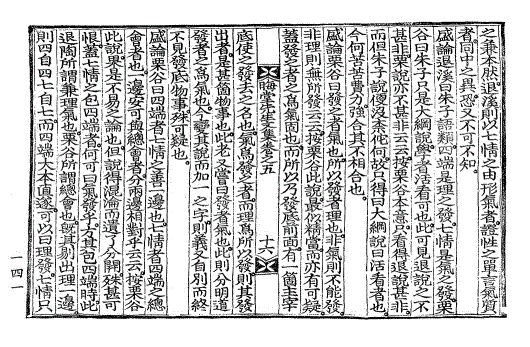 之兼本然。退溪则以七情之由形气者。證性之单言气质者。同中之异。恐又不可不知。
之兼本然。退溪则以七情之由形气者。證性之单言气质者。同中之异。恐又不可不知。盛论退溪曰朱子语类。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栗谷曰朱子只是大纲说。学者活看可也。此可见退说之不甚非。栗说亦不甚非云云。按栗谷本意。只看得退说甚非。而但朱子说便没柰佗何。故只得曰大纲说曰活看者也。今何苦苦费力。强合其不相合也。
盛论栗谷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云云。按栗谷此说。最似精当。而亦有可疑。盖发之者之为气固也。而所以乃发底前面。有一个主宰底使之发去之名也。气为发之者。而理为所以发。则其发出者。是甚个物事也。此老又尝曰发者气也。此则分明道发者之为气也。今变其说而加一之字。则义又自别而终不见发底物事。殊可疑也。
盛论栗谷曰四端者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者四端之总会者也。一边安可与总会者。分两边相对乎云云。按栗谷此说。果是不易之论也。但说得混沦而遗了分开。殊甚可恨。盖七情之包四端者。何可曰气发乎。方其包四端时。此退陶所谓兼理气也。栗谷所谓总会也。既其剔出理一边。则四自四七自七。而四端大本直遂。可以曰理发。七情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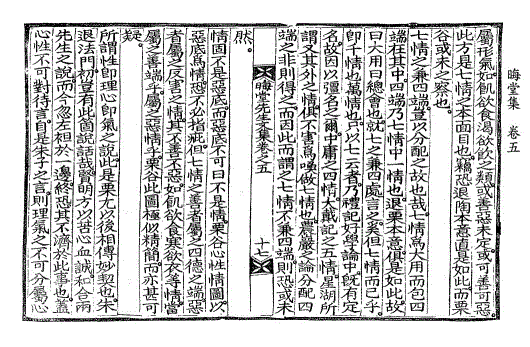 属形气。如饥欲食渴欲饮之类。或善恶未定。或可善可恶。此方是七情之本面目也。窃恐退陶本意直是如此。而栗谷或未之察也。
属形气。如饥欲食渴欲饮之类。或善恶未定。或可善可恶。此方是七情之本面目也。窃恐退陶本意直是如此。而栗谷或未之察也。七情之兼四端。岂以分配之故也哉。七情为大用而包四端在其中。四端乃七情中一情也。退栗本意。俱是如此。故曰大用曰总会也。就七之兼四处言之。奚但七情而已乎。即千情也万情也。只以七云者。乃礼记好学论中。既有定名。故因以彊名之尔。中庸之四情。大戴记之五情。星湖所谓又其外之情。俱不害为唤做七情也。农岩之论分配四端之非则得之。而因此而谓之七情不兼四端。则恐或未然。
情固不是恶底。而恶底不可曰不是情。栗谷心性情图。以恶底为情。恐不必指疵。但七情之善者属之四德之端。恶者属之反害之情。其不善不恶。如饥欲食寒欲衣等情。当属之善端乎。属之恶情乎。栗谷此图极似精简。而亦甚可疑。
所谓性即理心即气之说。此是栗尤以后相传妙契也。朱退法门。初岂有此个说话哉。贤明方以苦心血诚。和合两先生之说。而今忽左袒于一边。终恐其不济于此事也。盖心性不可对待言。自是朱子之言。则理气之不可分属心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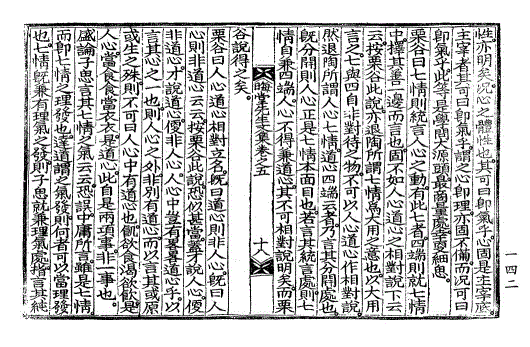 性。亦明矣。况心之体性也。其可曰即气乎。心固是主宰底。主宰者其可曰即气乎。谓之心即理。亦固不备。而况可曰即气乎。此等是学问大源头。最商量处。幸更细思。
性。亦明矣。况心之体性也。其可曰即气乎。心固是主宰底。主宰者其可曰即气乎。谓之心即理。亦固不备。而况可曰即气乎。此等是学问大源头。最商量处。幸更细思。栗谷曰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云云。按栗谷此说。亦退陶所谓七情为大用之意也。以大用言之。七与四自非对待之物。不可以人心道心作相对说。然退陶所谓人心七情。道心四端云者。乃言其分开处也。既分开则人心正是七情本面目也。若言其统言处。则七情自兼四端。人心不得兼道心。其不可相对说明矣。而栗谷说得之矣。
栗谷曰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云云。按栗谷此说。恐似甚当。盖才说人心。便非道心。才说道心。便非人心。人心中岂有略略道心乎。以言其心之一也。则人心之外。非别有道心。而以言其或原或生之殊。则不可曰人心中有道心也。饥欲食渴欲饮。是人心。当食食当衣衣。是道心。此自是两项事。非一事也。
盛论子思言其七情之气云云。恐误。中庸所言。虽是七情。而即七情之理发也。达道谓之气发。则何者可以当理发也。七情既兼有理气之发。则子思就兼理气处。指言其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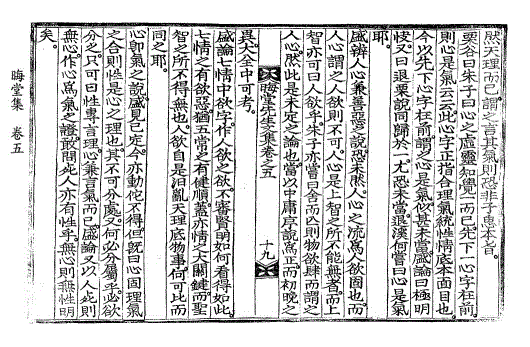 然天理而已。谓之言其气则恐非子思本旨。
然天理而已。谓之言其气则恐非子思本旨。栗谷曰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云云。此心字正指合理气统性情底本面目也。今以先下心字在前。谓之心是气。似甚未当。盛论曰极明快。又曰退栗说同归于一。尤恐未当。退溪何尝曰心是气耶。
盛辨人心兼善恶之说。恐未然。人心之流为人欲固也。而人心谓之人欲则不可。人心是上智之所不能无者。而上智亦可曰人欲乎。朱子亦尝曰舍而亡则物欲肆而谓之人心。然此是未定之论也。当以中庸序说为正。而初晚之异。大全中可考。
盛论七情中欲字。作人欲之欲。不审贤明如何看得如此。七情之有欲恶。犹五常之有健顺。盖亦情之大关键。而圣智之所不得无也。人欲自是汩乱天理底物事。何可比而同之耶。
心即气之说。盛见已定。今亦动佗不得。但既曰心固理气之合则性是心之理也。其不可分处。又何必分属乎。必欲分之。只可曰性专言理。心兼言气而已。盛论又以人死则无心。作心为气之證。敢问死人亦有性乎。无心则无性明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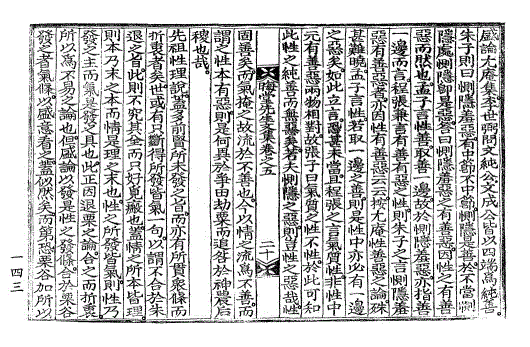 盛论尤庵集。李世弼问文纯公,文成公皆以四端为纯善。朱子则曰恻隐羞恶。有中节不中节。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答曰恻隐羞恶之有善恶。因性之有善恶而然也。孟子言性善。取善一边。故于恻隐羞恶。亦指善一边而言。程张兼言有善有恶之性。则朱子之言恻隐羞恶有善恶者。亦因性有善恶云云。按尤庵性善恶之论。殊甚难晓。孟子言性。若取一边之善。则是性中亦必有一边之恶矣。如此立言。恐甚未当。且程张之言气质性。非性中元有善恶两物相对。故张子曰气质之性不性。于此可知此性之纯善而无恶矣。若夫恻隐之恶。则岂性之恶哉。性固善矣。而气掩之故流于不善也。今以情之流为不善。而谓之性本有恶。则是何异于争田劫粟而追咎于神农后稷也哉。
盛论尤庵集。李世弼问文纯公,文成公皆以四端为纯善。朱子则曰恻隐羞恶。有中节不中节。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答曰恻隐羞恶之有善恶。因性之有善恶而然也。孟子言性善。取善一边。故于恻隐羞恶。亦指善一边而言。程张兼言有善有恶之性。则朱子之言恻隐羞恶有善恶者。亦因性有善恶云云。按尤庵性善恶之论。殊甚难晓。孟子言性。若取一边之善。则是性中亦必有一边之恶矣。如此立言。恐甚未当。且程张之言气质性。非性中元有善恶两物相对。故张子曰气质之性不性。于此可知此性之纯善而无恶矣。若夫恻隐之恶。则岂性之恶哉。性固善矣。而气掩之故流于不善也。今以情之流为不善。而谓之性本有恶。则是何异于争田劫粟而追咎于神农后稷也哉。先祖性理说。盖多前贤所未发之旨。而亦有所贯众条而折衷者矣。世或有只断得所发皆气一句。以谓不合于朱退之旨。此则不究其全而只好觅瘢也。盖情之所本皆理。则本乃末之本而情是理之末也。性之所发皆气。则性乃发之主而气是发之具也。此正因退栗之论。合之而折衷。所以为不易之论也。但盛论以发是性之发条。合于栗谷发之者气条。以盛意看之。盖似然矣。而第恐栗谷加所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4H 页
 字于发字上。似或与发是性之发云者。有相不同。幸更商焉。
字于发字上。似或与发是性之发云者。有相不同。幸更商焉。答都礼叔
别纸尽多综覈肯綮。而第观盛意。以英亦南之人也。其言有若攻排栗说者然。此则殊不尽人之意也。愚初间先得栗说而读之。次读退说。二说莫知适从。而被栗说先横肚里。意未尝不在于栗说也。最后参以先祖之说。意有所会而疑有所质。虽不敢妄是非先辈。而亦尝自有所折衷焉。于栗说则取其混沦而看得发处分明。于退说则取其主理而说得分劈尤备。苟有人妄论栗说而遽加攻斥。则愚将竭力而攻之矣。夫何暇以党同伐异之心。以乱天下公共底义理也。盖栗翁未尝曰理是死物也。且如理通气局之论。亦未尝见理不明。然只以理看作无为无用之物。则是终未免徒拥虚号。而所谓乘气而发者。毕竟 赶马之驮醉人也。此则不得无千载之疑。而所以不敢专信者也。今公尊信栗说。求所以执领而平看者。夫孰曰不可。而但与人讲究。不要遽伸己说。必尽其人之意。只求其是非得失之归可也。与西人言。先疑其攻退说。与南人言。先疑其攻栗说。则恐不能济事也。所驳诸条。别纸录去。幸视至而更驳之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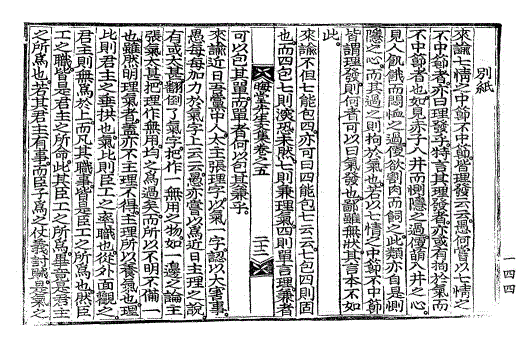 别纸
别纸来谕七情之中节不中节。皆理发云云。愚何尝以七情之不中节者。亦曰理发乎。特言其理发者。亦或有拘于气而不中节者也。如见赤子入井而恻隐之过。便萌入井之心。见人饥饿而闷恤之过。便欲割肉而饲之。此类亦自是恻隐之心。而其过之则拘于气也。若以七情之中节不中节皆谓理发。则何者可以曰气发也。鄙虽无状。其言本不如此。
来谕不但七能包四。亦可曰四能包七云云。七包四则固也。而四包七则深恐未然。七则兼理气。四则单言理。兼者可以包其单。而单者何以包其兼乎。
来谕近日吾党中人。太主张理字。以气一字。认以大害事。愚每每加力于气字上云云。愚亦尝以为近日主理之说。有或太甚。翻倒了气字。把作一无用之物。如一边之论主张气太甚。把理作无用。均之为过矣。而所以不明不备一也。虽然明理气者。盖亦不主理不得。主理所以养气也。理比则君主之垂拱也。气比则臣工之率职也。从外面观之。君主则无为于上。而凡其职事。皆是臣工之所为也。然臣工之职。皆是君主之所命。此其臣工之所为。毕竟是君主之所为也。若其君主有事。而臣子为之仗义讨贼。是气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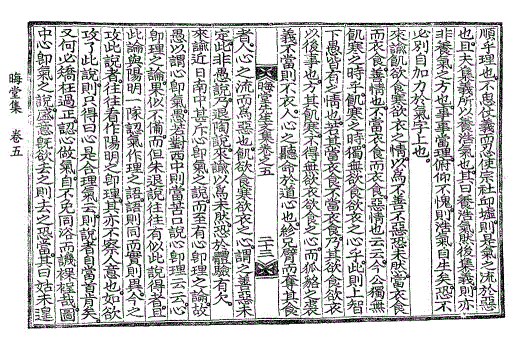 顺乎理也。不思仗义而忍使宗社邱墟。则是气之流于恶也。且夫集义所以养浩气也。其曰养浩气然后集义。则亦非养气之方也。事事当理。俯仰不愧。则浩气自生矣。恐不必别自加力于气字上也。
顺乎理也。不思仗义而忍使宗社邱墟。则是气之流于恶也。且夫集义所以养浩气也。其曰养浩气然后集义。则亦非养气之方也。事事当理。俯仰不愧。则浩气自生矣。恐不必别自加力于气字上也。来谕饥欲食寒欲衣之情。以为不善不恶恐未然。当衣食而衣食。善情也。不当衣食而衣食。恶情也云云。今公独无饥寒之时乎。饥寒之时。独无欲食欲衣之心乎。此则上智下愚皆有之情也。若其当衣食不当衣食。乃其欲食欲衣以后事也。方其饥寒。不得无欲衣欲食之心。而狐貉之裘义不当则不衣。人心之听命于道心也。紾兄臂而夺其食者。人心之流而为恶也。饥欲食寒欲衣之心。谓之善恶未定。此非愚说。乃退陶说。来谕以为未然。恐于体验有欠。
来谕近日南中甚斥心即气之说。而至有心即理之论。故愚以谓心即气。愚若对西中则当苦口说心即理云云。心即理之论。果似不备。而但朱退说往往有似此说得者。且此论与阳明一队认气作理之语。语则同而实则异。今之攻此说者。往往看作阳明之即理。其亦不察人意也。如欲攻了此说。则只得曰心是合理气云。则说者自当首肯矣。又何必矫枉过正。认心做气。自不免同浴而讥裸裎哉。图中心即气之说。盛意既欲去之则去之恐当。其曰姑未遑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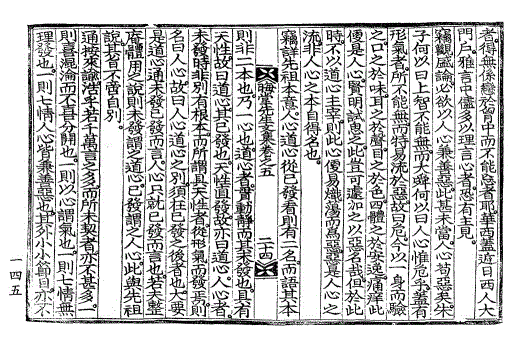 者。得无系恋于胸中而不能忘者耶。华西盖近日西人大门户。雅言中尽多以理言心者。恐有主见。
者。得无系恋于胸中而不能忘者耶。华西盖近日西人大门户。雅言中尽多以理言心者。恐有主见。窃观盛论。必欲以人心兼善恶。此甚未当。人心苟恶矣。朱子何以曰上智不能无。而大舜何以曰人心惟危乎。盖有形气者。所不能无。而特易流于恶。故曰危。今以一身而验之。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四体之于安逸。痛痒此便是人心。贤明试思之。此岂可遽加之以恶名哉。但于此时。不以道心主宰。则此心便易炽荡而为恶。恶是人心之流。非人心之本自得名也。
窃详先祖本意。人心道心从已发看则有二名。而语其本则非二本也。乃一心也。道心者。贯动静而其未发也。具有天性。故曰道心。其已发也。天性直发。故亦曰道心。人心者。未发时非别有根本。而所谓具天性者。从形气而发焉。则名曰人心。故曰人心道心之别。须在已发之后者也。大要是道心通未发已发而言。人心只就已发而言也。若夫整庵体用之说则未发谓之道心。已发谓之人心。此与先祖说。其旨不啻自别。
通按来谕。浩乎若千万言之多。而所未契者。亦不甚多。一则喜混沦而不喜分开也。一则以心谓气也。一则七情无理发也。一则七情人心皆兼善恶也。其外小小节目。亦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6H 页
 足道也。愚之所录。非曰退说是而栗说非也。亦非曰栗说是而退说非也。亦非欲高明之舍旧见而从我也。其是非得失之归则将俟千载之公议而已。盖理气之说甚博。诸儒之辨不一。后学见之。仁者谓之仁。智者谓之智。种下生种。各立己见。其说愈多而其弊日滋。吾辈之讲明此理。所不可自已。而大略观先辈说。得其要领而后。可语其归趣。欲得其要领。则退说之主理。栗说之混沦。先祖说之分合。皆其大题也。但退说一转则理气各立而太极将离了阴阳。栗说一转则此理沦于空寂而将为天下无用之物。先祖说一转则理气为一物而将至于指太极为阴阳。此等处。须细心着眼。勿以私意害之然后。可以有济于此事也。今盛录见得未尝不精切。而苟或主此以往则虽无太极赤立之弊。而将或至于此理之沦于空寂。此则明者之所当自省也。
足道也。愚之所录。非曰退说是而栗说非也。亦非曰栗说是而退说非也。亦非欲高明之舍旧见而从我也。其是非得失之归则将俟千载之公议而已。盖理气之说甚博。诸儒之辨不一。后学见之。仁者谓之仁。智者谓之智。种下生种。各立己见。其说愈多而其弊日滋。吾辈之讲明此理。所不可自已。而大略观先辈说。得其要领而后。可语其归趣。欲得其要领。则退说之主理。栗说之混沦。先祖说之分合。皆其大题也。但退说一转则理气各立而太极将离了阴阳。栗说一转则此理沦于空寂而将为天下无用之物。先祖说一转则理气为一物而将至于指太极为阴阳。此等处。须细心着眼。勿以私意害之然后。可以有济于此事也。今盛录见得未尝不精切。而苟或主此以往则虽无太极赤立之弊。而将或至于此理之沦于空寂。此则明者之所当自省也。答都礼叔别纸
来谕高峰总论末段曰七情兼有理气之发。此是高峰说未尽处也。愚欲改之曰七情兼有理气则似或无碍。退溪于此段。何不明白辨论。而只曰烂漫同归也。退溪于理发之发字。恐或偶未照管云云。高峰说则曰未尽而欲改。退溪说则曰偶失照管。似未稳当。愚意高峰七情兼有理气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6L 页
 发一段。退溪既许其同归。则此实退陶之定论也。
发一段。退溪既许其同归。则此实退陶之定论也。来谕性理之发。有不从形气而直发者。有由形气而发者。然则性之发有两样耶云云。性理之发。果有不从形气而直发者。贤明之大惊小怪。看作大不是。恐亦贤者之不察也。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若理无自动。则周子必曰生阳而动。既言动而生阳。则其自动可知也。朱子曰以流行言则太极有动静。又曰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此非太极之自动静耶。退溪曰理发而气随之。所谓理发。非理之自发耶。理既有自动静。则其有不待气而自发者。固昭然矣。然世无无气之理。非气则理无挂搭处。是故理虽自发。然其发则必发在形气上而气为之资具也。此周子所谓生阳生阴也。朱子所谓理有安顿也。退溪所谓气随也。栗谷所谓发之者气也。吾先祖所谓须关形气也。然则无论四与七。发处无非气也。然四端之发。纯然是天理而不落在形气之私。故曰不从形气。虽曰不从形气而气自随则固也。特理不随气也。今如盛说则是四端也从形气。七情也从形气。顾何有四七之分乎。朱子之曰或原或生。又何也。请更加少商焉。理无为三字。果是鄙人之疑案也。盖尝言之。理何尝有为耶。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然使尧舜而一切端拱。真个无为。则是不过陈后主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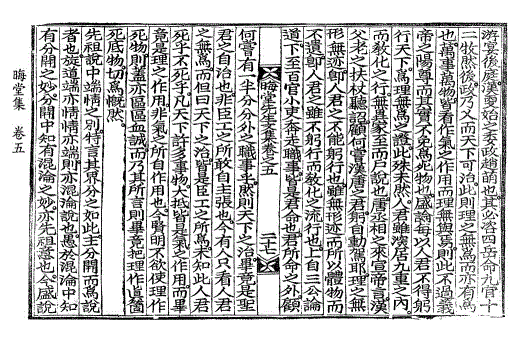 游宴后庭。汉更始之委政赵萌也。其必咨四岳命九官十二牧然后。政乃乂而天下可治。此则理之无为而亦有为也。万事万物。皆看作气之作用而理无与焉。则此不过义帝之阳尊而其实不免为死物也。盛论每以人君不得躬行天下。为理无为之證。此殊未然。人君虽深居九重之内。而教化之行。无异家至而户说也。唐丞相之来宣帝言。汉父老之扶杖听诏。顾何尝汉唐之君。躬自动驾耶。理之无形无迹。即人君之不能躬行也。虽无形迹而所以体物而不遗。即人君之虽不躬行而教化之流行也。上自三公论道。下至百官小吏奔走职事。皆是君命也。君所命之外。顾何尝有一半分分外之职事乎。然则天下之治。毕竟是圣君之自治也。非臣工之所敢自主张也。今有人只看人君之无为。而但曰天下之治。皆是臣工之所为。未知此人君死乎不死乎。凡天下许多事物。大抵皆是气之作用。而毕竟是理之作用。非气之所自作用也。今贤明不欲使理作死物。则盖亦区区血诚。而乃其所言则毕竟把理作真个死底物。切为慨然。
游宴后庭。汉更始之委政赵萌也。其必咨四岳命九官十二牧然后。政乃乂而天下可治。此则理之无为而亦有为也。万事万物。皆看作气之作用而理无与焉。则此不过义帝之阳尊而其实不免为死物也。盛论每以人君不得躬行天下。为理无为之證。此殊未然。人君虽深居九重之内。而教化之行。无异家至而户说也。唐丞相之来宣帝言。汉父老之扶杖听诏。顾何尝汉唐之君。躬自动驾耶。理之无形无迹。即人君之不能躬行也。虽无形迹而所以体物而不遗。即人君之虽不躬行而教化之流行也。上自三公论道。下至百官小吏奔走职事。皆是君命也。君所命之外。顾何尝有一半分分外之职事乎。然则天下之治。毕竟是圣君之自治也。非臣工之所敢自主张也。今有人只看人君之无为。而但曰天下之治。皆是臣工之所为。未知此人君死乎不死乎。凡天下许多事物。大抵皆是气之作用。而毕竟是理之作用。非气之所自作用也。今贤明不欲使理作死物。则盖亦区区血诚。而乃其所言则毕竟把理作真个死底物。切为慨然。先祖说中端情之别。特言其界分之如此。主分开而为说者也。旋道端亦情情亦端。则亦混沦说也。愚于混沦中知有分开之妙。分开中知有混沦之妙。亦先祖意也。今盛说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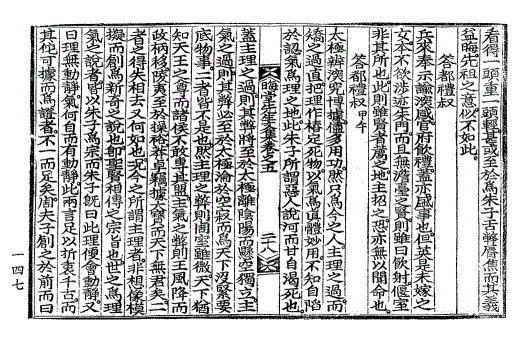 看得一头重一头轻。甚或至于为朱子舌弊唇焦而其义益晦。先祖之意。似不如此。
看得一头重一头轻。甚或至于为朱子舌弊唇焦而其义益晦。先祖之意。似不如此。答都礼叔
兵来奉示谕深感。官府饮礼。盖亦盛事也。但英是未嫁之女。本不欲涉迹朱门。而且无澹台之贤。则虽曰饮射。偃室非其所也。此则虽贤者荐之。地主招之。恐亦无以闻命也。
答都礼叔(甲午)
太极辨深究博据。尽多用功。然只为今之人。主理之过。而矫之过直。把理作桩定死物。以气为真体妙用。不知自陷于认气为理之地。此朱子所谓恶人说河而甘自渴死也。盖主理之过。则其弊将至于太极离阴阳而悬空独立。主气之过。则其弊必至于太极沦于空寂而为天下没紧要底物事。二者皆不是也。然主理之弊则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天王之尊而诸侯不敢专其盟。主气之弊则王风降而政柄移。陵夷至于操,裕,莽,卓窃据大宝而天下无君矣。二者之得失相去又何如也。况今之所谓主理者。非想像模拟而创为新奇之说也。即圣贤相传之宗旨也。世之为理气之说者。皆以朱子为宗。而朱子既曰此理便会动静。又曰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此两言足以折衷千古。而其佗可据而为證者。不一而足矣。周夫子创之于前而曰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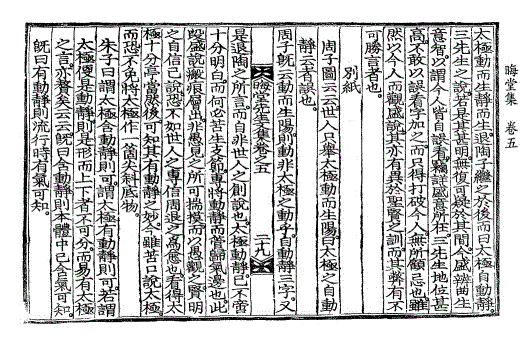 太极动而生静而生。退陶子继之于后而曰太极自动静。三先生之说。若是其甚明。无复可疑于其间。今盛辨曲生意智。以谓今人皆自误看。窃详盛意所在。三先生地位甚高。不敢以误看字加之。而只得打破今人。无所顾忌也。虽然以今人而观盛说。其亦有异于圣贤之训。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也。
太极动而生静而生。退陶子继之于后而曰太极自动静。三先生之说。若是其甚明。无复可疑于其间。今盛辨曲生意智。以谓今人皆自误看。窃详盛意所在。三先生地位甚高。不敢以误看字加之。而只得打破今人。无所顾忌也。虽然以今人而观盛说。其亦有异于圣贤之训。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也。别纸
周子图云云。世人只举太极动而生阳。曰太极之自动静云者误也。
周子既云动而生阳。则动非太极之动乎。自动静三字。又是退陶之所言。而自非世人之创说也。太极动静。已不啻十分明白。而何必苦生支节。专将动静而管归气边也。此段盛说瘢痕层出。非愚见之所可揣摸。而以愚观之。贤明之自信己说。恐不如世人之专信周退之为愈也。看得太极十分亭当然后。可知其有动静之妙。今虽苦口说太极。而恐不免将太极作一个尖斜底物。
朱子曰谓太极含动静则可。谓太极有动静则可。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云云。既曰含动静则本体中已含气可知。既曰有动静则流行时有气可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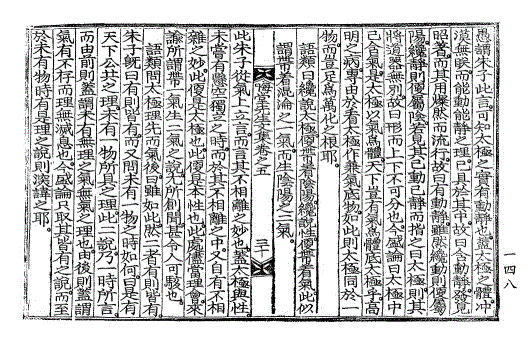 愚谓朱子此言。可知太极之实有动静也。盖太极之体。冲漠无眹。而能动能静之理。已具于其中。故曰含动静。发见昭著。而其用灿然而流行。故曰有动静。虽然才动则便属阳。才静则便属阴。若见其已动已静而指之曰太极。则其将道器无别。故曰形而上下不可分也。今盛论曰太极中已含气。是太极以气为体。天下岂有气为体底太极乎。高明之病。专由于看太极作兼气底物。如此则太极同于一物。而岂足为万化之根耶。
愚谓朱子此言。可知太极之实有动静也。盖太极之体。冲漠无眹。而能动能静之理。已具于其中。故曰含动静。发见昭著。而其用灿然而流行。故曰有动静。虽然才动则便属阳。才静则便属阴。若见其已动已静而指之曰太极。则其将道器无别。故曰形而上下不可分也。今盛论曰太极中已含气。是太极以气为体。天下岂有气为体底太极乎。高明之病。专由于看太极作兼气底物。如此则太极同于一物。而岂足为万化之根耶。语类曰才说太极。便带着阴阳。才说性。便带着气。此似谓带着混沦之一气。而生阴阳之二气。
此朱子从气上立言。而言其不相离之妙也。盖太极与性。未尝有悬空独立之时。而于其不相离之中。又自有不相杂之妙。此便是太极也。此便是本性也。此处尽当理会。来谕所谓带一气生二气之说。尤所创闻。甚令人可骇也。
语类问太极理先而气后。曰虽如此。然二者有则皆有。
朱子既曰有则皆有。而又问未有一物之时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此二说。乃一时所言。而由前则盖谓未有无理之气无气之理也。由后则盖谓气有不存而理无灭息也。今盛论只取其皆有之说。而至于未有物时有是理之说则深讳之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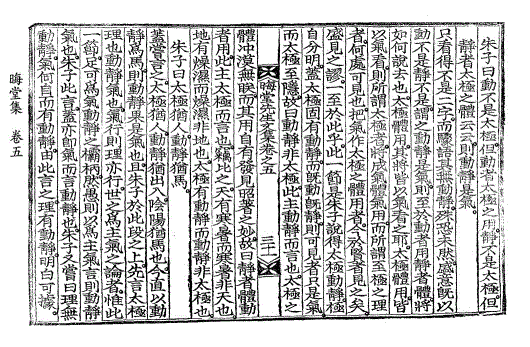 朱子曰动不是太极。但动者太极之用。静不是太极。但静者太极之体云云。则动静是气。
朱子曰动不是太极。但动者太极之用。静不是太极。但静者太极之体云云。则动静是气。只看得不是二字。而骤语其无动静。殊恐未然。盛意既以动不是静不是。谓之动静是气。则至于动者用静者体。将如何说去也。太极体用。其将皆以气看之耶。太极体用。皆以气看。则所谓太极者。将成气体气用。而所谓至极之理者。何处可见也。把气作太极之体用者。今于贤者见之矣。盛见之谬。一至于此乎。此一节是朱子说得太极动静。极自分明。盖太极固有动静。而既动既静。则可见者只是气。而太极至隐。故曰动静非太极。此主动静而言也。太极之体冲漠无眹。而其用自有发见昭著之妙。故曰静者体动者用。此主太极而言也。窃比之。天有寒暑而寒暑非天也。地有燥湿而燥湿非地也。太极有动静而动静非太极也。
朱子曰太极犹人。动静犹马。
盖尝言之。太极犹人。动静犹出入。阴阳犹马也。今直以动静为马。则动静果是气也。且朱子于此段之上。先言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世之为主气之论者。惟此一节。足可为气动静之把柄。然愚则以为主气言则动静气也。朱子此言。盖亦即气而言动静也。朱子又尝曰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由此言之。理有动静。明白可据。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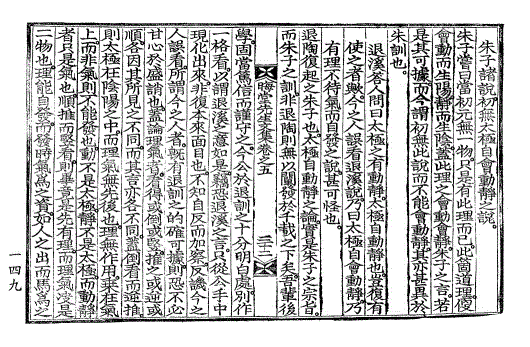 朱子诸说。初无太极自会动静之说。
朱子诸说。初无太极自会动静之说。朱子尝曰当初元无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个道理。便会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盖此理之会动会静。朱子之言。若是其可据。而今谓初无此说而不能会动静。其亦甚异于朱训也。
退溪答人问曰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岂复有使之者欤。今之人误看退溪说。乃曰太极自会动静。乃有理不待气而自发之说。甚可怪也。
退陶复起之朱子也。太极自动静之论。实是朱子之宗旨。而朱子之训。非退陶则无以阐发于千载之下矣。吾辈后学。固当笃信而谨守之。今公于退训之十分明白处。别作一格看。以谓退溪之意如是。窃恐退溪之言。只从公手中现化出来。非复本来面目也。不知自反而加察。反讥今之人误看。所谓今之人者。既有退训之的确可据。则恐不必甘心于盛诮也。盖论理气者。看得或倒或竖。推之或逆或顺。各因其所见之不同。而其言亦各不同。盖倒看而逆推。则太极在阴阳之中。而理气无先后也。理无作用。乘在气上。而非气则不能发也。动不是太极。静不是太极。而动静者只是气也。顺推而竖看。则毕竟是先有理。而理气决是二物也。理能自发。而发时气为之资。如人之出而马为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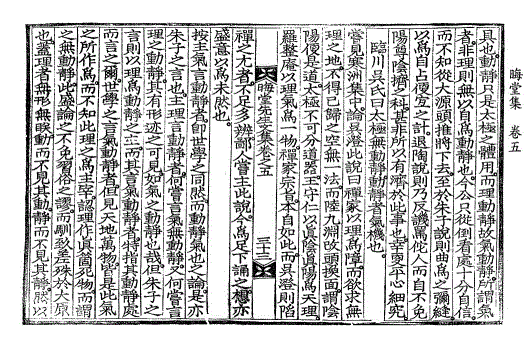 具也。动静只是太极之体用。而理动静故气动静。所谓气者。非理则无以自为动静也。今公只从倒看处十分自信。而不知从大源头推将下去。至于朱子说则曲为之弥缝。以为自占便宜之计。退陶说则乃反讥骂佗人而自不免阳尊阴挤之科。甚非所以有济于此事也。幸更平心细究。
具也。动静只是太极之体用。而理动静故气动静。所谓气者。非理则无以自为动静也。今公只从倒看处十分自信。而不知从大源头推将下去。至于朱子说则曲为之弥缝。以为自占便宜之计。退陶说则乃反讥骂佗人而自不免阳尊阴挤之科。甚非所以有济于此事也。幸更平心细究。临川吴氏曰太极无动静。动静者气机也。
尝见寒洲集中。论吴澄此说曰禅家以理为障。而欲求无理之地。不得已归之空无一法。而陆九渊改头换面。谓阴阳便是道。太极不可分道器。王守仁以真阴真阳为天理。罗整庵以理气为一物。禅家宗旨。本自如此。而吴澄则陷禅之尤者。不足多辨。鄙人尝主此说。今为足下诵之。想亦盛意以为未然也。
按主气言动静者。即世学之同然。而动静气也之论。是亦朱子之言也。主理言动静者。何尝言气无动静。又何尝言理之动静。其有形迹之可见。如气之动静也哉。但朱子之言则以理为动静之主。而其言气动静者。特指其动静处而言之尔。世学之言气动静者。但见天地万物。皆是此气之所作为。而不知此理之为主宰。认理作真个死物。而谓之无动静。此盛论之不免习俗之谬。而驯致差殊于大原也。盖理者无形无眹。动而不见其动。静而不见其静。然以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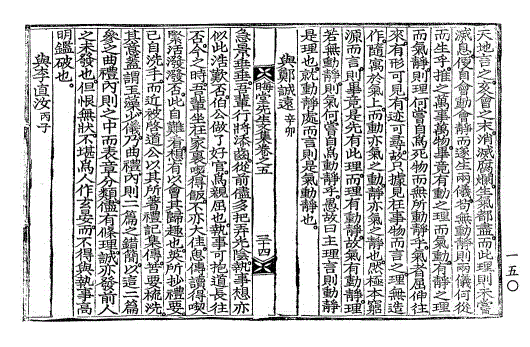 天地言之。亥会之末。消灭腐烂。生气都尽。而此理则未尝灭息。便自会动会静而遂生两仪。苟无动静则两仪何从而生乎。推之万事万物。毕竟有动之理而气动。有静之理而气静。则理何尝自为死物而无所动静乎。气者屈伸往来。有形可见。有迹可寻。故只据见在事物而言之。理无造作。随寓于气上。而动亦气之动。静亦气之静也。然极本穷源而言。则毕竟是先有此理。而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理若无动静。则气何尝自为动静乎。愚故曰主理言则动静是理也。就动静处而言则是气动静也。
天地言之。亥会之末。消灭腐烂。生气都尽。而此理则未尝灭息。便自会动会静而遂生两仪。苟无动静则两仪何从而生乎。推之万事万物。毕竟有动之理而气动。有静之理而气静。则理何尝自为死物而无所动静乎。气者屈伸往来。有形可见。有迹可寻。故只据见在事物而言之。理无造作。随寓于气上。而动亦气之动。静亦气之静也。然极本穷源而言。则毕竟是先有此理。而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理若无动静。则气何尝自为动静乎。愚故曰主理言则动静是理也。就动静处而言则是气动静也。与郑诚远(辛卯)
急景垂垂。吾辈行将添齿。从前尽多把弄光阴。执事想亦似此浩叹否。伯公做了好官。为亲屈也。执事可抱道长往否。今之时。吾辈坐在家里吃得饭。不亦大佳。思传读得吃紧活泼泼否。此自难看。想有以会其归趣也。英所抄礼要。已自洗手。而近被启道公以其所著礼记集传。苦要梳洗。其意盖谓玉藻,少仪。乃曲礼,内则二篇之错简。以这二篇参之曲礼,内则之中而表章分类。尽有条理。诚亦发前人之未发也。但恨无状。不堪为人作玄晏。而不得与执事高明鉴破也。
与李直汝(丙子)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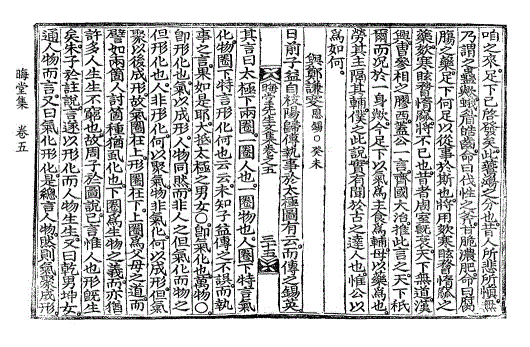 咱之来。足下已启发矣。此燕鸿之分也。昔人所悲所慎。无乃谓之蛊欤。蛾眉皓齿。命曰伐性之斧。甘脆浓肥。命曰腐肠之药。足下何足以从事于斯也。将用欬寒眩瞀惰窳之药。欬寒眩瞀惰窳。将不已也。昔者周室既衰。天下无道。汉兴。曹参相之胶西。盖公一言。齐国大治。推此言之。天下秖尔。而况于一身欤。今足下以气为主食为辅。毋以药为也。劳其主隔其辅。仆之此说。实有闻于古之达人也。惟公以为如何。
咱之来。足下已启发矣。此燕鸿之分也。昔人所悲所慎。无乃谓之蛊欤。蛾眉皓齿。命曰伐性之斧。甘脆浓肥。命曰腐肠之药。足下何足以从事于斯也。将用欬寒眩瞀惰窳之药。欬寒眩瞀惰窳。将不已也。昔者周室既衰。天下无道。汉兴。曹参相之胶西。盖公一言。齐国大治。推此言之。天下秖尔。而况于一身欤。今足下以气为主食为辅。毋以药为也。劳其主隔其辅。仆之此说。实有闻于古之达人也。惟公以为如何。与郑谦叟(恩锡○癸未)
日前子益自枝阳归传执事于太极图有云。而传之锡英。其言曰太极下两圈。一圈人也。一圈物也。人圈下特言气化。物圈下特言形化何也云云。未知子益传之不误。而执事之言。果如是耶。大抵太极之男女○。即气化也。万物○。即形化也。气以成形。人物同然。而非人之但气化而物之但形化也。人非形化。何以聚气。物非气化。何以成形。但气聚以后成形。故气圈在上。形圈在下。上圈为父母之道。而譬如两个人讨个种犹虱化也。下圈为生物之义。而亦犹许多人生生不穷也。故周子于图说。已言惟人也形既生矣。朱子于注说。言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又曰乾男坤女。通人物而言。又曰气化形化。是总言人物。然则气聚成形。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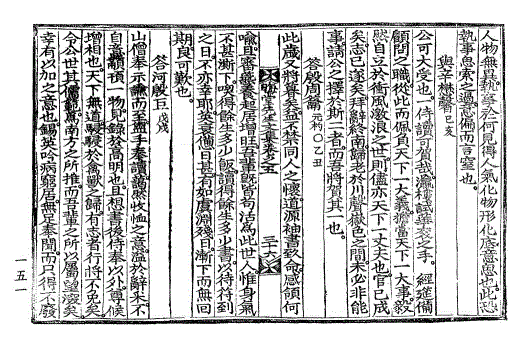 人物无异。执事于何见得人气化物形化底意思也。此恐执事思索之过。意偏而言窒也。
人物无异。执事于何见得人气化物形化底意思也。此恐执事思索之过。意偏而言窒也。与辛懋馨(己亥)
公可大受也。一侍读可贺哉。瀛楼试华衮之手。 经筵备顾问之职。从此而佩负天下一大义。担当天下一大事。毅然自立于冲风激浪之世。则尽亦天下一丈夫也。官已成矣。志已遂矣。拜辞终南。归老于川声岳色之间。未必非能事。请公之择于斯二者。而吾将贺其一也。
答殷周籥(元杓○乙丑)
此岁又将暮矣。益不禁同人之怀。道源袖书致命。感领何喻。且审燕养起居增旺。吾辈既皆苟活为此世人。惟身气不甚渐下。吃得馀生多少饭。读得馀生多少书。以待符到之日。不亦幸耶。英衰惫日甚。有如虞渊残日。渐下而无回期。良可叹也。
答河殷巨(戊戌)
山僧奉示谕而至。盥手奉读。蔼然收恤之意。溢于辞采。不自意颟顸一物。见录于高明也。且想书后侍奉以外。尊候增相也。天下无道。骎骎于禽兽之归。有志者行将不免矣。令公世其儒范。为南方之所推。而吾辈之所以属望深矣。幸有以加之意也。锡英吟病穷居。无足奉闻。而只得不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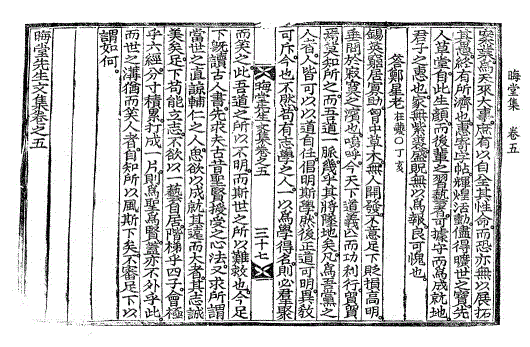 案业。为天来大事。庶有以自全其性命。而恐亦无以展拓其愚。终有所济也。惠寄字帖。辉煌活动。尽得旷世之宝。先人草堂。自此生颜。而后辈之习艺者。可据守而为成就地。君子之惠也。家无紫裘。盛贶无以为报。良可愧也。
案业。为天来大事。庶有以自全其性命。而恐亦无以展拓其愚。终有所济也。惠寄字帖。辉煌活动。尽得旷世之宝。先人草堂。自此生颜。而后辈之习艺者。可据守而为成就地。君子之惠也。家无紫裘。盛贶无以为报。良可愧也。答郑星老(在夔○丁亥)
锡英穷居寡助。胸中草木。无人开发。不意足下贬损高明。垂问于寂寞之滨也。呜呼。今天下道义亡而功利行。贸贸焉莫知所之。而吾道一脉。几乎其将坠地矣。凡为吾党之人者。人皆可以以道自任。倡明斯学。然后正道可明。异教可斥。今也不然。苟有志学之人。一以为学得名。则必群聚而笑之。此吾道之所以不明。而斯世之所以难救也。今足下既读古人书。先求夫古昔圣贤授受之心法。又求所谓当世之直谅辅仁之人。思欲以成就其远而大者。其志诚美矣。足下苟能立志。不欲以一艺自居。阶梯乎四子。会极乎六经。分寸积累。打成一片。则为圣为贤。盖亦不外乎此。而世之沟犹而笑人者。自知所以风斯下矣。不审足下以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