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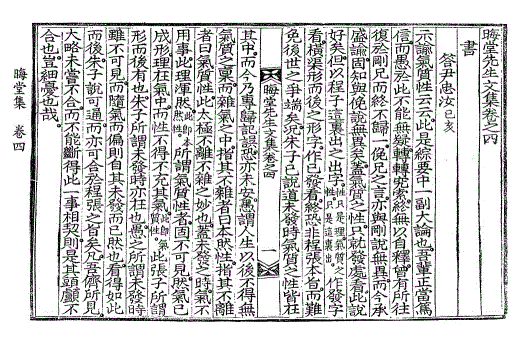 答尹忠汝(己亥)
答尹忠汝(己亥)示谕气质性云云。此是综要中一副大论也。吾辈正当笃信。而愚于此不能无疑。转转究索。终无以自释。曾有所往复于刚兄而终不归一。俛兄之言。亦与刚说无异。而今承盛谕。固知与俛说无异矣。盖气质之性。只就发处看。此说好矣。但以程子这里出之出字。(性只是理。气质之性。只是这里出。)作发字看。横渠形而后之形字。作已发看。终恐非程张本旨。而难免后世之争端矣。况朱子已说道未发时气质之性皆在其中。而今乃专归记误。恐亦未安。愚谓人生以后不得无气质之禀。而杂气之中。指其不杂者曰本然性。指其不离者曰气质性。此太极不离不杂之妙也。盖未发之时。气不用事。此理浑然。(此即本然性。)所谓气质性者。固不可见。然气已成形。理在气中。而性不得不充其气。(此即气质性。)此张子所谓形而后有也。朱子所谓未发时亦在也。愚之所谓未发时虽不可见。而随气而偏则自其未发而已然也。看得如此而后。朱子说可通。而亦可合于程张之旨矣。凡吾侪所见。大略未尝不合。而不能断得此一事相契。则是其头颅不合也。岂细忧也哉。
答安吉叟(己亥)
便中承示谕缕缕。贬辱至此。三复甚感。记昔云泥殊迹。相见未易。老来觉得有相契者。而但恨地不撤远。无由得痛相切磨。以开发胸中草木也。旱魃告菑。人情嗷嗷。如令兄食人者也。齐敖之忧。想有大于区区但谋口腹者也。锡英年间无一事做得。日暮道远。恐亦终无以藉手于朋友也。俛宇果有 召旨。而其出处自不干他人事。第观渠意。惟恐沼鱼之不深。时义则盖亦然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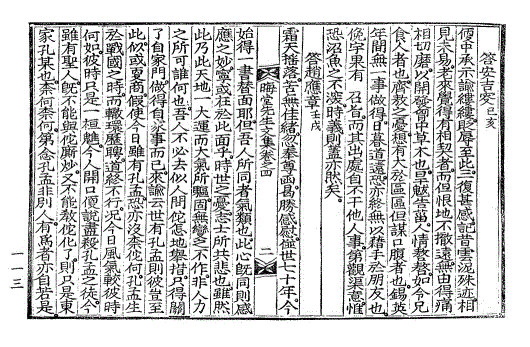 答赵应章(壬戌)
答赵应章(壬戌)霜天摇落。苦无佳绪。忽奉尊函。曷胜感慰。并世七十年。今始得一书替面耶。但吾人所同者气类也。此心既同则感应之妙。宁或在于此面乎。时世之忧。志士所共悲也。虽然此乃此天地一大运而大气所驱。固无变之不作。非人力之所可谁何也。吾人不必去似人问佗怎地举措。只得关了自家门。做得自家事而已。来谕云世有孔孟则彼岂至此。似或更商。假使今日虽有孔孟。恐亦没柰佗何。孔孟生于战国之时。而辙环历聘。道终不行。况今日风气较彼时何如。彼时只是一桓魋。今人开口便说尽杀孔孟之徒。今虽有圣人。既不能与佗厮炒。又不能教佗化了。则只是东家孔某也。柰何柰何。第念孔孟非别人。有为者亦自若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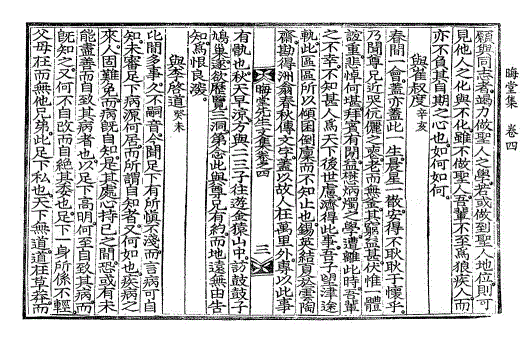 愿与同志者。竭力做圣人之学。若或做到圣人地位。则可见他人之化与不化。虽不做圣人。吾辈不至为狼疾人。而亦不负其自期之心也。如何如何。
愿与同志者。竭力做圣人之学。若或做到圣人地位。则可见他人之化与不化。虽不做圣人。吾辈不至为狼疾人。而亦不负其自期之心也。如何如何。与崔叔度(辛亥)
春间一会。盖亦盖此一生。晨星一散。安得不耿耿于怀乎。乃闻尊兄近哭伉俪之丧。老而无釜。其穷益甚。伏惟一体谊重。悲悼何堪。拜宾有閒。益懋炳烛之学。遭离此时。吾辈之不幸。不知甚人为天下后世虑。济得此事。吾子望津途轨。此区区所以倾囷倒廪而不知止也。锡英结夏于云陶斋。勘得洲翁春秋传文字。盖以故人在万里外。专以此事有骫也。秋天早凉。方与二三子往游金猿山中。访鼓鼓子鸠巢。遂欲历览三洞。第念此与尊兄有约。而地远无由告知。为恨良深。
与李启道(癸未)
比间多事。久不嗣音。今闻足下有所慎不浅。而言病可自知。未审足下病源何居。而所谓自知者。又何如也。疾病之来。人固难免。而病既自知。是其处心持己之间。恐或有未能尽善而自致其病者也。以足下高明。何至自致其病。而既知之。又何不自改而自绝其委也。足下一身所系不轻。父母在而无他兄弟。此足下私也。天下无道。道在草莽。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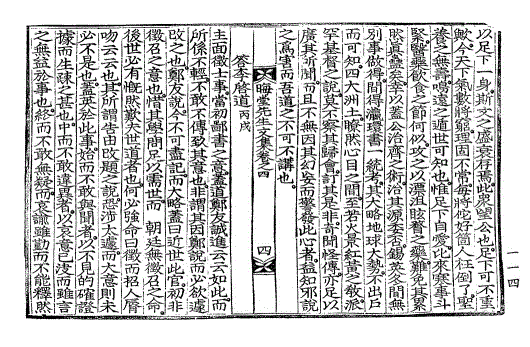 以足下一身。斯文之盛衰存焉。此众望公也。足下可不重欤。今天下气数将穷。理固不常。每将佗好个人枉倒了。圣养之无寿。鸣远之遁世可知也。惟足下自爱。比来寒事斗紧。医药饮食之节何似。攻之以漂沮眩瞀之药。难免其累然真蛊矣。幸以盖公治齐之术。治其源委否。锡英冬间无别事做得。间得瀛环书一统考。其大略地球大势。不出户而可知。四大洲土。瞭然心目之间。至若火景红黄之教。派罕基督之说。莫不察其归会。订其是非。奇闻怪传。亦足以广其所闻。而且不无因其幻妄而警发此心者。益知邪说之为害而吾道之不可不讲也。
以足下一身。斯文之盛衰存焉。此众望公也。足下可不重欤。今天下气数将穷。理固不常。每将佗好个人枉倒了。圣养之无寿。鸣远之遁世可知也。惟足下自爱。比来寒事斗紧。医药饮食之节何似。攻之以漂沮眩瞀之药。难免其累然真蛊矣。幸以盖公治齐之术。治其源委否。锡英冬间无别事做得。间得瀛环书一统考。其大略地球大势。不出户而可知。四大洲土。瞭然心目之间。至若火景红黄之教。派罕基督之说。莫不察其归会。订其是非。奇闻怪传。亦足以广其所闻。而且不无因其幻妄而警发此心者。益知邪说之为害而吾道之不可不讲也。答李启道(丙戌)
主面徵士事。当初鄙书之意。盖道郑友诚进云云如此。而所系不轻。不敢不传致其意也。非谓其因郑说而必欲遽改之也。郑友说。今不可尽记。而大略盖曰近世此官。初非徵召之意也。惜其学问足以需世。而 朝廷无徵召之命。后世必有慨然叹夫世道者也。何必强命曰徵而招人唇吻云云也。其所谓告由改题之说。恐涉太遽。而大意则未必不是也。盖英于此事。始而不敢与闻者。以不见的确證据而生疏之甚也。中而不敢违异者。以哀意已决而虽言之无益于事也。终而不敢无疑。而哀谕虽勤而不能释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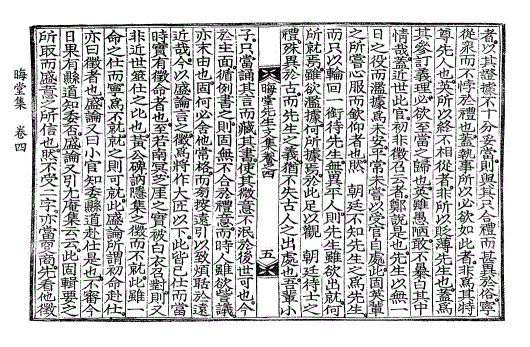 者。以其證据不十分妥当。则与其只合礼而甚异于俗。宁从众而不悖于礼也。盖执事所以必欲如此者。非为其特尊先人也。英所以终不相从者。非所以贬薄先生也。盖为其参订义理。必欲至当之归也。英虽愚陋。敢不㬥白其中情哉。盖近世此官。初非徵召云者。郑说是也。先生以无一日之役而滥据为未安。平常未尝以受官自处。此固英辈之所尝心服而钦仰者也。然 朝廷不知先生之为先生。而只以轮回一衔待先生。无异平人。则先生虽欲出就。何所就焉。虽欲滥据。何所据焉。于此足以观 朝廷待士之礼。殊异于古。而先生之义。犹不失古人之出处也。吾辈小子。只当诵其言而藏其书。使其微意不泯于后世可也。今于主面。循例书之。则固无不合于礼意。而时人虽欲訾议。亦末由也。固何必舍他常格。而旁搜远引以致烦聒于远近哉。今以盛论言之。徵为将作大匠以下。此皆已仕而当时实有徵命者也。至若南冥,芝厓之实被白衣召对。则又非近世筮仕之比也。黄公碑,讷隐集之徵而不就。此虽一命之仕而宁为不就。就之则可就。此盛论所谓初命赴仕。亦曰徵者也。盛论又曰小官知委县道赴仕是也。不审今日果有县道知委否。盛论又引尤庵集云云。此固辑要之所取而盛意之所信也。然不受二字。亦当更商。先看他徵
者。以其證据不十分妥当。则与其只合礼而甚异于俗。宁从众而不悖于礼也。盖执事所以必欲如此者。非为其特尊先人也。英所以终不相从者。非所以贬薄先生也。盖为其参订义理。必欲至当之归也。英虽愚陋。敢不㬥白其中情哉。盖近世此官。初非徵召云者。郑说是也。先生以无一日之役而滥据为未安。平常未尝以受官自处。此固英辈之所尝心服而钦仰者也。然 朝廷不知先生之为先生。而只以轮回一衔待先生。无异平人。则先生虽欲出就。何所就焉。虽欲滥据。何所据焉。于此足以观 朝廷待士之礼。殊异于古。而先生之义。犹不失古人之出处也。吾辈小子。只当诵其言而藏其书。使其微意不泯于后世可也。今于主面。循例书之。则固无不合于礼意。而时人虽欲訾议。亦末由也。固何必舍他常格。而旁搜远引以致烦聒于远近哉。今以盛论言之。徵为将作大匠以下。此皆已仕而当时实有徵命者也。至若南冥,芝厓之实被白衣召对。则又非近世筮仕之比也。黄公碑,讷隐集之徵而不就。此虽一命之仕而宁为不就。就之则可就。此盛论所谓初命赴仕。亦曰徵者也。盛论又曰小官知委县道赴仕是也。不审今日果有县道知委否。盛论又引尤庵集云云。此固辑要之所取而盛意之所信也。然不受二字。亦当更商。先看他徵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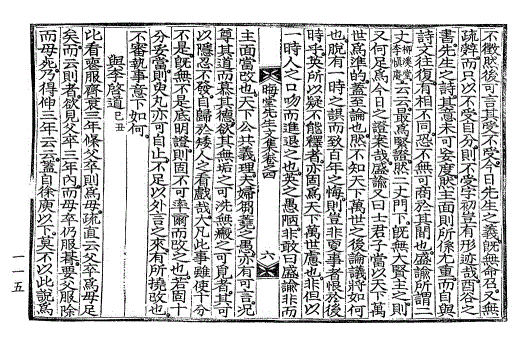 不徵然后可言其受不受。今日先生之义。既无命召。又无疏辞。而只以不受自分。则不受字初岂有形迹哉。酉谷之书。先生之诗。其意未可妄度。然主面则所系尤重。而自与诗文往复。有相不同。恐不无可商于其间也。盛谕所谓二丈(柳溪堂,李慎庵。)云云。最为紧證。然二丈门下。既无大贤主之。则又何足为今日之證案哉。盛谕又曰士君子当以天下万世为准的。盖至论也。然不知天下万世之后论议将如何也。脱有一时之误而致百年之悔。则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乎。英所以疑不能释者。亦固为天下万世虑也。非但以一时人之口吻而进退之也。英之愚陋。非敢曰盛谕非而主面当改也。天下公共义理。夫妇刍荛之愚。亦有可言。况尊其道而慕其德。欲其无垢之可洗无瘢之可觅者。其可以隐忍不发。自归于矮人之看戏哉。大凡此事虽使十分不是。既无不是底明證。则固不可率尔而改之也。若固十分妥当。则臾丸亦可自止。不足以外言之来。有所挠改也。不审执事意下如何。
不徵然后可言其受不受。今日先生之义。既无命召。又无疏辞。而只以不受自分。则不受字初岂有形迹哉。酉谷之书。先生之诗。其意未可妄度。然主面则所系尤重。而自与诗文往复。有相不同。恐不无可商于其间也。盛谕所谓二丈(柳溪堂,李慎庵。)云云。最为紧證。然二丈门下。既无大贤主之。则又何足为今日之證案哉。盛谕又曰士君子当以天下万世为准的。盖至论也。然不知天下万世之后论议将如何也。脱有一时之误而致百年之悔。则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乎。英所以疑不能释者。亦固为天下万世虑也。非但以一时人之口吻而进退之也。英之愚陋。非敢曰盛谕非而主面当改也。天下公共义理。夫妇刍荛之愚。亦有可言。况尊其道而慕其德。欲其无垢之可洗无瘢之可觅者。其可以隐忍不发。自归于矮人之看戏哉。大凡此事虽使十分不是。既无不是底明證。则固不可率尔而改之也。若固十分妥当。则臾丸亦可自止。不足以外言之来。有所挠改也。不审执事意下如何。与李启道(己丑)
比看丧服齐衰三年条父卒则为母。疏直云父卒为母足矣。而云则者。欲见父卒三年内。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伸三年云云。盖自徐庾以下。莫不以此说为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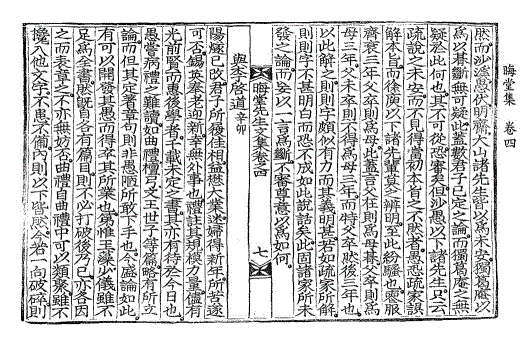 然。而沙溪,愚伏,明斋,大山诸先生皆以为未安。独葛庵以为以期断无可疑。此盖数君子已定之论。而独葛庵之无疑于此何也。其不可从。恐审矣。但沙愚以下诸先生。只云疏说之未安。而不见得当初本旨之不然者。愚恐疏家误解本旨。而徐庾以下诸先辈莫之辨明。至此纷骚也。丧服齐衰三年父卒则为母。此盖言父在则为母期。父卒则为母三年。父未卒则不得为母三年。而特父卒然后三年也。以此解之。则则字颇似有力而其义明甚。若如疏家所解。则则字不甚明白而恐不成如此说话矣。此固诸家所未发之论。而妄以一言为断。不审尊意以为如何。
然。而沙溪,愚伏,明斋,大山诸先生皆以为未安。独葛庵以为以期断无可疑。此盖数君子已定之论。而独葛庵之无疑于此何也。其不可从。恐审矣。但沙愚以下诸先生。只云疏说之未安。而不见得当初本旨之不然者。愚恐疏家误解本旨。而徐庾以下诸先辈莫之辨明。至此纷骚也。丧服齐衰三年父卒则为母。此盖言父在则为母期。父卒则为母三年。父未卒则不得为母三年。而特父卒然后三年也。以此解之。则则字颇似有力而其义明甚。若如疏家所解。则则字不甚明白而恐不成如此说话矣。此固诸家所未发之论。而妄以一言为断。不审尊意以为如何。与李启道(辛卯)
阳燧已改。君子所履佳相。益懋大业。迷妇得新年。所苦遂可否。锡英奉老迎新。幸无外事也。礼注其规模力量。尽有光前贤而惠后学者。千载未定之书。其亦有待于今日也。愚尝病礼之难读。如曲礼,檀弓,文王世子等篇。略有所立论。而但其定著章句则非愚陋所敢下手也。今盛论如此。有可以开发其愚而得卒其所业也。第惟玉藻,少仪虽不足为全书。然既自各有篇目。则不必打破后乃已。亦各因之而表章之。不亦无妨否。曲礼自曲礼中可以类聚。虽不搀入他文字。不患不备。内则以下皆然。今若一向破碎。则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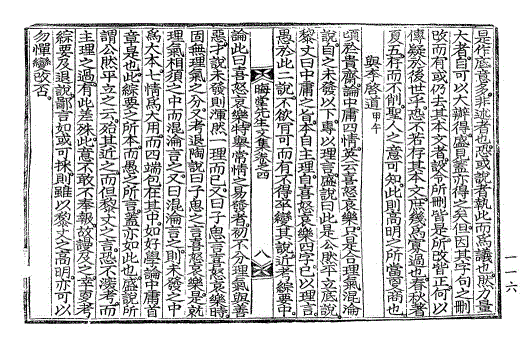 是作底意多。非述者也。恐或说者执此而为议也。然力量大者。自可以大办得。盛见盖亦得之矣。但因其字句之删改而有或仍去其本文者。设令所删皆是。所改皆正。何以传疑于后世乎。恐不若存其本文。庶几为寡过也。春秋著夏五。存而不削。圣人之意可知。此则高明之所当更商也。
是作底意多。非述者也。恐或说者执此而为议也。然力量大者。自可以大办得。盛见盖亦得之矣。但因其字句之删改而有或仍去其本文者。设令所删皆是。所改皆正。何以传疑于后世乎。恐不若存其本文。庶几为寡过也。春秋著夏五。存而不削。圣人之意可知。此则高明之所当更商也。与李启道(甲午)
顷于贵斋。论中庸四情。英云喜怒哀乐。只是合理气混沦说。自之未发以下。专以理言。盛说曰此是公然平立底说。黎丈曰中庸之旨。本自主理。自喜怒哀乐四字。已以理言。愚于此二说。不欲肯可而有不得卒变其说。近考综要中。论此曰喜怒哀乐。特举常情之易发者。初不分理气与善恶。才说未发则浑然一理而已。又曰子思言喜怒哀乐时。固无理气之分。又考退陶说曰子思之言喜怒哀乐。是就理气相须之中而混沦言之。又曰混沦言之。则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而四端包在其中。如好学论中庸首章是也。此综要之所本。而愚之所言。盖亦如此也。盛说所谓公然平立之云。殆其近之。而但黎丈之言。恐不深考。而主理之过。有此差殊。此意不敢不奉报。故谩及之。幸更考综要及退说。鄙言如或可采。则虽以黎丈之高明。亦可以勿惮变改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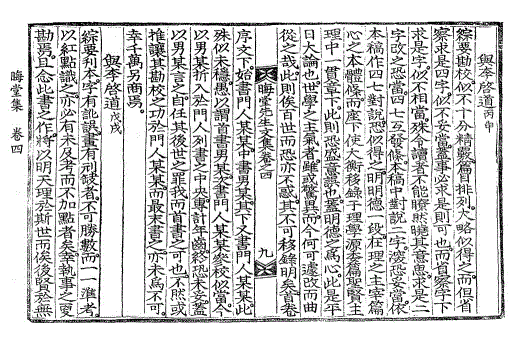 与李启道(丙申)
与李启道(丙申)综要勘校。似不十分精覈。篇目排列。大略似得之。而但省察求是四字。似不妥当。盖事必求是则可也。而省察字下求是字。似不相当。殊令读者不能瞭然晓其意思。求是二字改之恐当。四七互发条。本稿中对说二字。深恐妥当。依本稿作四七对说。恐似得之。明明德一段。在理之主宰篇心之本体条。而座下使大衡移录于理学源委篇圣贤主理中一贯章下。此则恐盛意误也。盖明德之为心。此是平日大论也。世学之主气者。虽或惊异。而今何可遽改而曲从之哉。此则俟百世而恐亦不惑。其不可移录明矣。首卷序文下。始书门人某某。中书男某。其下又书门人某某。此殊似未稳。愚以谓首书男某。次书门人某某参校似当。今以男某折入于门人列书之中央。专计年齿。终恐未妥。盖以男某言之。自任其后世之罪我而首书之可也。不然或推让其勘校之功于门人某某。而最末书之。亦未为不可。幸千万另商焉。
与李启道(戊戌)
综要刊本。字有讹误。画有刓缺者。不可胜数。而一一准考。以红点识之。亦必有未及考而不加点者矣。幸执事之更勘焉。且念此书之作。将以明天理于斯世而俟后贤于无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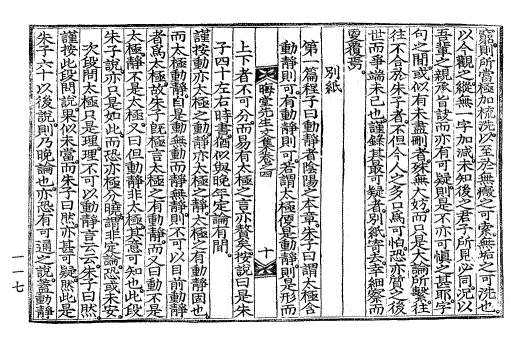 穷。则所当极加梳洗。以至于无瘢之可索。无垢之可洗也。以今观之。纵无一字加减。未知后之君子所见必同。况以吾辈之亲承旨诀而亦有可疑。则是不亦可慎之甚耶。字句之间。或似有未尽删者。殊无大妨。而只是大论所系。往往不合于朱子者。不但今人之多口为可怕。恐亦质之后世而争端未已也。谨录其最可疑者。别纸寄去。幸细察而更覆焉。
穷。则所当极加梳洗。以至于无瘢之可索。无垢之可洗也。以今观之。纵无一字加减。未知后之君子所见必同。况以吾辈之亲承旨诀而亦有可疑。则是不亦可慎之甚耶。字句之间。或似有未尽删者。殊无大妨。而只是大论所系。往往不合于朱子者。不但今人之多口为可怕。恐亦质之后世而争端未已也。谨录其最可疑者。别纸寄去。幸细察而更覆焉。别纸
第一篇程子曰动静者阴阳之本章。朱子曰谓太极含动静则可。有动静则可。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按说曰是朱子四十左右时书。犹似与晚年定论有间。
谨按动亦太极之动。静亦太极之静。太极之有动静固也。而太极动静。自是动无动而静无静。则不可以目前动静者为太极。故朱子既极言太极之有动静。而又曰动不是太极。静不是太极。又曰但动静非太极。其意可知也。此段朱子说。亦只是如此。而恐亦极分晓。谓非定论。恐或未安。
次段问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云云。朱子曰然。
谨按此段问说。果似未当。而朱子曰然。亦甚可疑。然此是朱子六十以后说。则乃晚论也。亦恐有可通之说。盖动静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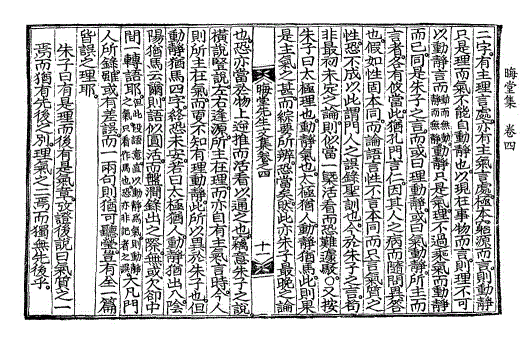 二字。有主理言处。亦有主气言处。极本穷源而言。则动静只是理而气不能自动静也。以现在事物而言。则理不可以动静言而(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动静只是气。理不过乘气而动静而已。同是朱子之言。而或曰理动静。或曰气动静。所主而言者。各有攸当。此犹孔门言仁。因其人之病而随问异答也。假如性固本同。而论语言性不言本同而只言气质之性。恐不成以此谓门人之误录圣训也。今于朱子之言。苟非最初未定之论。则似当一槩活看而恐难遽驳。○又按朱子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此则果是主气之甚。而综要所辨。恐当矣。然此亦朱子最晚之论也。恐亦当于物上逆推而活看以通之也。窃意朱子之说。横说竖说。左右逢源。所主在理。而亦自有主气言时。今人则所主在气。而更不知有理动静。此所以异于朱子也。但动静犹马四字。终恐未安。若曰太极犹人。动静犹出入。阴阳犹马云尔。则语似圆活。而盘涧录出之际。无或欠却中间一转语耶。(但此段语意。直以动静为气。则动静之气。只看作马也。恐亦非记者之误。)大凡门人所录。虽或有差误。而一两句则犹可听莹。岂有全一篇皆误之理耶。
二字。有主理言处。亦有主气言处。极本穷源而言。则动静只是理而气不能自动静也。以现在事物而言。则理不可以动静言而(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动静只是气。理不过乘气而动静而已。同是朱子之言。而或曰理动静。或曰气动静。所主而言者。各有攸当。此犹孔门言仁。因其人之病而随问异答也。假如性固本同。而论语言性不言本同而只言气质之性。恐不成以此谓门人之误录圣训也。今于朱子之言。苟非最初未定之论。则似当一槩活看而恐难遽驳。○又按朱子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此则果是主气之甚。而综要所辨。恐当矣。然此亦朱子最晚之论也。恐亦当于物上逆推而活看以通之也。窃意朱子之说。横说竖说。左右逢源。所主在理。而亦自有主气言时。今人则所主在气。而更不知有理动静。此所以异于朱子也。但动静犹马四字。终恐未安。若曰太极犹人。动静犹出入。阴阳犹马云尔。则语似圆活。而盘涧录出之际。无或欠却中间一转语耶。(但此段语意。直以动静为气。则动静之气。只看作马也。恐亦非记者之误。)大凡门人所录。虽或有差误。而一两句则犹可听莹。岂有全一篇皆误之理耶。朱子曰有是理而后有是气章。考證后说曰气质之一焉而犹有先后之别。理气之二焉而独无先后乎。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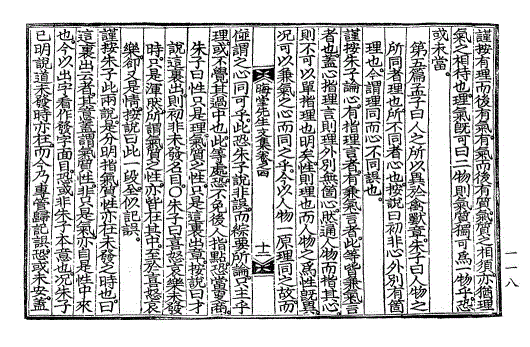 谨按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质。气质之相须。亦犹理气之相待也。理气既可曰二物则气质独可为一物乎。恐或未当。
谨按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质。气质之相须。亦犹理气之相待也。理气既可曰二物则气质独可为一物乎。恐或未当。第五篇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按说曰初非心外别有个理也。今谓理同而心不同误也。
谨按朱子论心。有指理言者。有兼气言者。此等皆兼气言者也。盖心指理言则理外别无个心。然通人物而指其心。则不可以单指理也明矣。性则理也而人物之为性既异。况可以兼气之心而同之乎。今以人物一原理同之故。而并谓之心同可乎。此恐朱子说非误。而综要所论。只主乎理。或不觉其过中也。此等处。恐不免后人指点。恐当更商。
朱子曰性只是理。气质之性。只是这里出章。按说曰才说这里出。则初非未发名目。○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至于喜怒哀乐。却又是情。按说曰此一段。全似记误。
谨按朱子此两说。是分明指气质性亦在未发之时也。曰这里出云者。其意盖谓气质性。非只是气。亦自是性中来也。今以出字看作发字面目。恐或非朱子本意也。况朱子已明说道未发时亦在。而今乃专管归记误。恐或未安。盖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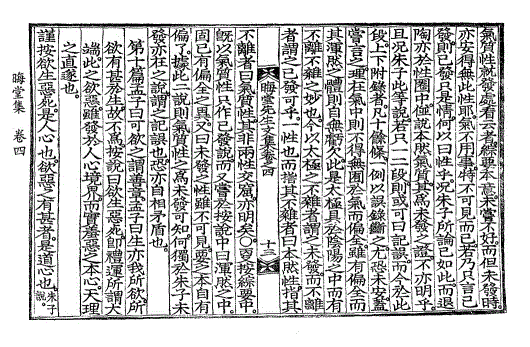 气质性就发处看云者。综要本意。未尝不好。而但未发时。亦安得无此性耶。气不用事。特不可见而已。若乃只言已发。则已发只是情。何以曰性乎。况朱子所论已如此。而退陶亦于性圈中。并说本然气质。其为未发之證。不亦明乎。且况朱子此等说。若只一二段。则或可曰记误。而今于此段。上下附录者。凡十馀条。一例以误录断之。尤恐未安。盖尝言之。理在气中则不得无囿于气而偏全。虽有偏全而其浑然之体则自无亏欠。此是太极具于阴阳之中而有不离不杂之妙也。今以太极之不杂者谓之未发。而不离者谓之已发可乎。一性也而指其不杂者曰本然性。指其不离者曰气质性。其非两性交窟。亦明矣。○更按综要中。既以气质性只作已发说。而又尝于按说中曰浑然之中。固已有偏全之异。又曰未发之性虽不可见。要之本自有偏了。据此二说则气质性之为未发可知。何独于朱子未发亦在之说。谓之记误也。恐亦自相矛盾也。
气质性就发处看云者。综要本意。未尝不好。而但未发时。亦安得无此性耶。气不用事。特不可见而已。若乃只言已发。则已发只是情。何以曰性乎。况朱子所论已如此。而退陶亦于性圈中。并说本然气质。其为未发之證。不亦明乎。且况朱子此等说。若只一二段。则或可曰记误。而今于此段。上下附录者。凡十馀条。一例以误录断之。尤恐未安。盖尝言之。理在气中则不得无囿于气而偏全。虽有偏全而其浑然之体则自无亏欠。此是太极具于阴阳之中而有不离不杂之妙也。今以太极之不杂者谓之未发。而不离者谓之已发可乎。一性也而指其不杂者曰本然性。指其不离者曰气质性。其非两性交窟。亦明矣。○更按综要中。既以气质性只作已发说。而又尝于按说中曰浑然之中。固已有偏全之异。又曰未发之性虽不可见。要之本自有偏了。据此二说则气质性之为未发可知。何独于朱子未发亦在之说。谓之记误也。恐亦自相矛盾也。第十篇孟子曰可欲之谓善章。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故不为。按说曰欲生恶死。即礼运所谓大端。此之欲恶。虽发于人心境界。而实羞恶之本心。天理之直遂也。
谨按欲生恶死。是人心也。欲恶之有甚者。是道心也。(朱子说。)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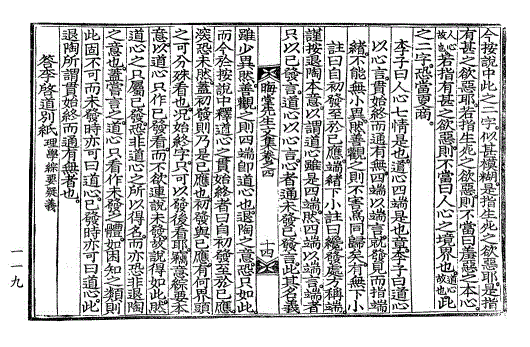 今按说中此之二字。似甚模糊。是指生死之欲恶耶。是指有甚之欲恶耶。若指生死之欲恶。则不当曰羞恶之本心。(人心故也。)若指有甚之欲恶。则不当曰人心之境界也。(道心故也。)此之二字。恐当更商。
今按说中此之二字。似甚模糊。是指生死之欲恶耶。是指有甚之欲恶耶。若指生死之欲恶。则不当曰羞恶之本心。(人心故也。)若指有甚之欲恶。则不当曰人心之境界也。(道心故也。)此之二字。恐当更商。李子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章。李子曰道心以心言。贯始终而通有无。四端以端言。就发见而指端绪。不能无小异。然善观之则不害为同归矣。有无下小注曰自初发至于已应。端绪下小注曰才发处方称端。
谨按退陶本意。以谓道心虽是四端。然四端以端言。端者只以已发言。道心以心言。心者通未发已发言。此其名义虽少异然。善观之则四端即道心也。退陶之意。恐只如此。而今于按说中释道心之贯始终者曰自初发至于已应。深恐未然。盖初发则乃是已应也。初发与已应。有何界头之可分殊看也。况始终字。只可以发后看耶。窃意综要本意。以道心只作已发看。而不欲连说未发。故说得如此。然道心之只属已发。恐非道心之所以得名。而亦恐非退陶之意也。盖尝言之。道心只看作未发之体。如困知之类则此固不可而未发时亦可曰道心。已发时亦可曰道心。此退陶所谓贯始终而通有无者也。
答李启道别纸(理学综要疑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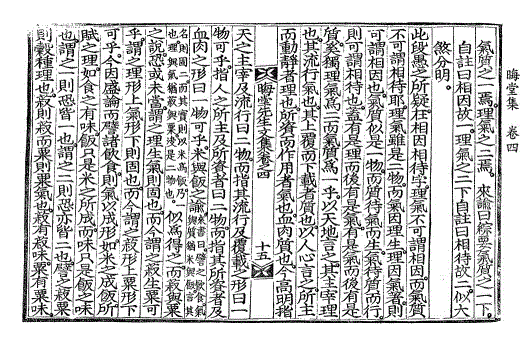 气质之一焉。理气之二焉。 来谕曰综要气质之一下。自注曰相因故一。理气之二下自注曰相待故二。似大煞分明。
气质之一焉。理气之二焉。 来谕曰综要气质之一下。自注曰相因故一。理气之二下自注曰相待故二。似大煞分明。此段愚之所疑。在相因相待字。理气不可谓相因。而气质不可谓相待耶。理气虽是二物。而气因理生。理因气著。则可谓相因也。气质似是一物。而质待气而生。气待质而行。则可谓相待也。盖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而后有是质。奚独理气为二而气质为一乎。以天地言之。其主宰理也。其流行气也。其上覆而下载者质也。以人心言之。所主而动静者理也。所资而作用者气也。血肉质也。今高明指天之主宰及流行曰二物。而指其流行及覆载之形曰一物可乎。指人之所主及所资者曰二物。而指其所资者及血肉之形曰一物可乎。米与饭之谕。(来书曰。譬之饮食。气与质犹米与饭。言其名则固二。而其实则以米为饭。乃一也。理与气犹菽与粟。决是二物也。)似为得之。而菽与粟之说。恐或未当。谓之理生气则固也。而今谓之菽生粟可乎。谓之理形上气形下则固也。而今谓之菽形上粟形下可乎。今因盛论而譬诸饮食。则气以成形。如米之成饭。所赋之理。如食之有味。饭只是米之所成。而味只是饭之味也。谓之一则恐皆一也。谓之二则恐亦皆二也。譬之菽粟则谷种理也。菽则菽而粟则粟气也。菽有菽味。粟有粟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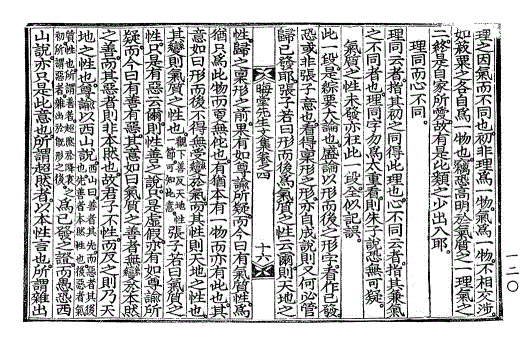 理之因气而不同也。初非理为一物。气为一物。不相交涉。如菽粟之各自为一物也。窃恐高明于气质之一理气之二。终是自家所爱。故有是比类之少出入耶。
理之因气而不同也。初非理为一物。气为一物。不相交涉。如菽粟之各自为一物也。窃恐高明于气质之一理气之二。终是自家所爱。故有是比类之少出入耶。理同而心不同。
理同云者。指其初之同得此理也。心不同云者。指其兼气之不同者也。理同字勿为太重看。则朱子说恐无可疑。
气质之性未发亦在此一段。全似记误。
此一段。是综要大论也。盛论以形而后之形字。看作已发。恐或非张子意也。看得禀形之形。亦自成说则又何必管归已发耶。张子若曰形而后为气质之性云尔。则天地之性。归之禀形之前。果有如尊谕所疑。而今曰有气质性。为犹只为此物而更无佗也。有犹本有一物而亦有此也。其意如曰形而后不得无受变于气。而其性则天地之性也。其变则气质之性也。(观下善反天地性一节。可知此意。)张子若曰气质之性。只是有恶云尔。则性善之说。只是虚假。亦有如尊谕所疑。而今曰有善有恶。其意如曰气质之善者无变于本然之善。而其恶者则非本然也。故君子不性。而反之则乃天地之性也。尊谕以西山说。(西山曰。善者其先。而恶者其后也。先善者本然性也。后恶者气质性也。所谓善者。超然于降衷之初。所谓恶者。杂出于既形之后。)为已发之證。而愚恐西山说。亦只是此意也。所谓超然者。以本性言也。所谓杂出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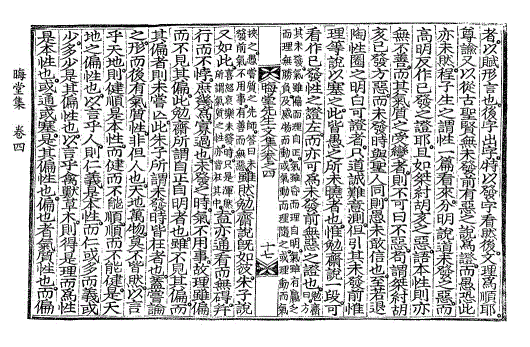 者。以赋形言也。后字出字。特以发字看然后。文理为顺耶。尊谕又以从古圣贤无未发前有恶之说为證。而愚恐此亦未然。程子生之谓性一篇看来。分明说道未发之恶。而高明反作已发之證耶。且如桀纣胡亥之恶。语本性则亦无不善。而其气质之受变者。则不可曰不恶。苟谓桀纣胡亥已发方恶。而未发时与圣人同。则愚未敢信也。至若退陶性圈之明白可證者。只道诚难意测。但引其未发前惟理等说以塞之。此皆愚之所未晓者也。惟勉斋说一段。可看作已发性之證左。而亦可为未发前无恶之證也。(勉斋曰。方其未发。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气虽有赢乏而理无胜负。及感物而动。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愚尝质之先师。答曰未发前气不用事。有善而无恶。)虽然勉斋说既如彼。朱子说又如此。(喜怒哀乐未发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盍亦通看而无碍。并行而不悖。庶几为寡过也。未发之时。气不用事。故理虽偏而不见其偏。此勉斋所谓自正自明者也。虽不见其偏。而其偏者则未尝亡。此朱子所谓未发时皆在者也。盖尝论之。形而后有气质性。非但人也。天地万物。莫不皆然。以言乎天地。则健顺是本性。而健而不能顺。顺而不能健。是天地之偏性也。以言乎人。则仁义是本性。而仁或多而义或少。多少是其偏性也。以言乎禽兽草木。则得是理而为性是本性也。或通或塞。是其偏性也。偏也者气质性也。而偏
者。以赋形言也。后字出字。特以发字看然后。文理为顺耶。尊谕又以从古圣贤无未发前有恶之说为證。而愚恐此亦未然。程子生之谓性一篇看来。分明说道未发之恶。而高明反作已发之證耶。且如桀纣胡亥之恶。语本性则亦无不善。而其气质之受变者。则不可曰不恶。苟谓桀纣胡亥已发方恶。而未发时与圣人同。则愚未敢信也。至若退陶性圈之明白可證者。只道诚难意测。但引其未发前惟理等说以塞之。此皆愚之所未晓者也。惟勉斋说一段。可看作已发性之證左。而亦可为未发前无恶之證也。(勉斋曰。方其未发。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气虽有赢乏而理无胜负。及感物而动。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愚尝质之先师。答曰未发前气不用事。有善而无恶。)虽然勉斋说既如彼。朱子说又如此。(喜怒哀乐未发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盍亦通看而无碍。并行而不悖。庶几为寡过也。未发之时。气不用事。故理虽偏而不见其偏。此勉斋所谓自正自明者也。虽不见其偏。而其偏者则未尝亡。此朱子所谓未发时皆在者也。盖尝论之。形而后有气质性。非但人也。天地万物。莫不皆然。以言乎天地。则健顺是本性。而健而不能顺。顺而不能健。是天地之偏性也。以言乎人。则仁义是本性。而仁或多而义或少。多少是其偏性也。以言乎禽兽草木。则得是理而为性是本性也。或通或塞。是其偏性也。偏也者气质性也。而偏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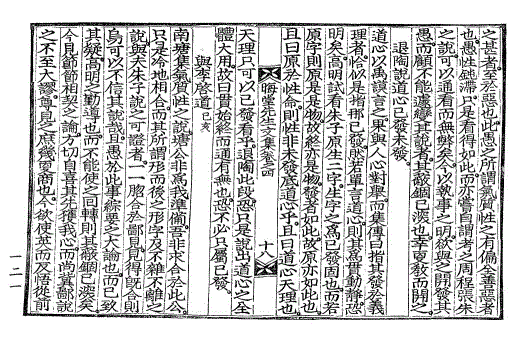 之甚者。至于恶也。此愚之所谓气质性之有偏全善恶者也。愚性钝滞。只是看得如此。而亦尝自谓考之周程张朱之说。可以通看而无弊矣。今以执事之明。欲与之开发其愚。而顾不能遽变其说者。其蔽锢已深也。幸更教而开之。
之甚者。至于恶也。此愚之所谓气质性之有偏全善恶者也。愚性钝滞。只是看得如此。而亦尝自谓考之周程张朱之说。可以通看而无弊矣。今以执事之明。欲与之开发其愚。而顾不能遽变其说者。其蔽锢已深也。幸更教而开之。退陶说道心已发未发。
道心以禹谟言之。果与人心对举。而集传曰指其发于义理者。恰似是指那已发。然若单言道心。则其为贯动静。恐明矣。高明试看朱子原生二字。生字之为已发固也。而若原字则原是是物。故终亦是物。发者如此。故原亦如此也。且曰原于性命。则性非未发底道心乎。且曰道心天理也。天理只可以已发看乎。退陶此段。恐只是说出道心之全体大用。故曰贯始终而通有无也。恐不必只属已发。
与李启道(己亥)
南塘集气质性之说。塘公非为我准备。吾非求合于此公。只是冷地相合。而其所谓形而后之形字及不杂不离之说。与夫朱子说之可證者。一一吻合于鄙见。见得既合则乌可以不信其说哉。且愚于此事综要之大论也。而已致其疑。高明之勤导也。而不能使之回转则其蔽锢已深矣。今见节节相契之论。方切自喜其先获我心。而尚冀鄙说之不至大谬。尊见之庶几更商也。今欲使英而反悟从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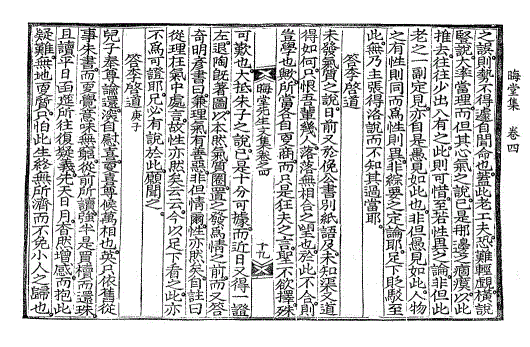 之误。则势不得遽自闻命也。盖此老工夫。恐难轻觑。横说竖说。大率当理。而但其心气之说。已是那边之痼瘼。以此推去。往往少出入有之。此则可惜。至若性异之论。非但此老之一副定见。亦自是愚见如此也。非但愚见如此。人物之有性则同而为性则异。非综要之定论耶。足下贬驳至此。无乃主张得洛说而不知其过当耶。
之误。则势不得遽自闻命也。盖此老工夫。恐难轻觑。横说竖说。大率当理。而但其心气之说。已是那边之痼瘼。以此推去。往往少出入有之。此则可惜。至若性异之论。非但此老之一副定见。亦自是愚见如此也。非但愚见如此。人物之有性则同而为性则异。非综要之定论耶。足下贬驳至此。无乃主张得洛说而不知其过当耶。答李启道
未发气质之说。日前又于俛公书别纸语及。未知渠又道得如何。只恨吾辈几人。落落无相合之望也。于此不合。则岂学也欤。所当各自更商。而只是狂夫之言。圣不欲择。殊可叹也。大抵朱子之说。已是十分可据。而近日又得一證左。退陶既著图。以本然气质圈。置之发为情之前。而又答奇明彦书曰。兼理气有善恶。非但情尔。性亦然矣。自注曰从理在气中处言。故性亦然矣云云。今以足下看之。此亦不为可證耶。兄必有说于此。愿闻之。
答李启道(庚子)
儿子奉尊谕还。深自慰喜。更喜尊候万相也。英只依旧从事朱书。而更觉意味无穷。从前所读。强半是买椟而还珠。且读平日函筵所往复疑义。先天日月。杳然增感。而抱此疑难。无地更质。只怕此生终无所济而不免小人之归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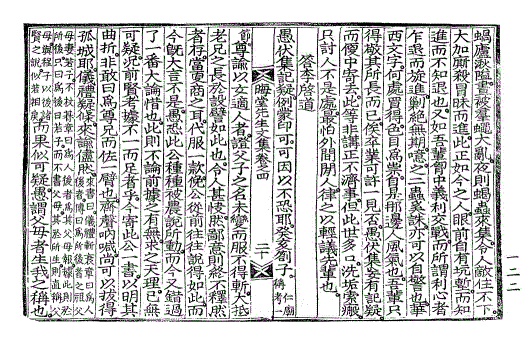 蜗庐湫隘。昼被群蝇大乱。夜则蝎虫来集。令人敌住不下。大加厮杀冒昧而进。此正如今之人。眼前自有坑堑。而知进而不知退也。又如吾辈胸中义利交战。而所谓利心者乍退而旋进。剿绝无期。噫。之二虫奚诛。亦可以自警也。华西文字。何处买得。色目为祟。自是那边人风气也。吾辈只得敬其所长而已。俟卒业可许一见否。愚伏集妄有记疑。而便中寄去。此等非讲正不济事。但此世多口。洗垢索瘢。只讨人不是处。最怕外间閒人。律之以轻议先辈也。
蜗庐湫隘。昼被群蝇大乱。夜则蝎虫来集。令人敌住不下。大加厮杀冒昧而进。此正如今之人。眼前自有坑堑。而知进而不知退也。又如吾辈胸中义利交战。而所谓利心者乍退而旋进。剿绝无期。噫。之二虫奚诛。亦可以自警也。华西文字。何处买得。色目为祟。自是那边人风气也。吾辈只得敬其所长而已。俟卒业可许一见否。愚伏集妄有记疑。而便中寄去。此等非讲正不济事。但此世多口。洗垢索瘢。只讨人不是处。最怕外间閒人。律之以轻议先辈也。答李启道
愚伏集记疑。例蒙印可。可因以不恐耶。癸亥劄子。( 仁庙称考一节。)尊谕以女适人者。證父子之名未变而服不得斩。大抵老兄之长于设譬如此也。令人甚快。然鄙意则终不释然者存。当更商之耳。代服一款。俛公从前往往说得如此。而今既大言不是。愚恐此公种种被农说所动。而今又错过了一番大论惜也。此则不论前据之有无。求之天理。已无可疑。况前贤考据不一而足者乎。今寄此公一书。以明其曲折。非敢曰为尊兄而佐一臂也。齐声呐喊。尚可以拔得孤城耶。仪礼疑条。来谕尽然。(来书曰。仪礼斩衰章曰为人后者。传曰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若子。不杖期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据此则于所后。只曰为后曰若子。而不书父母。其于所生。则直称父母。与程子以后诸贤之说。似若相戾。)而果似可疑。愚谓父母者生我之称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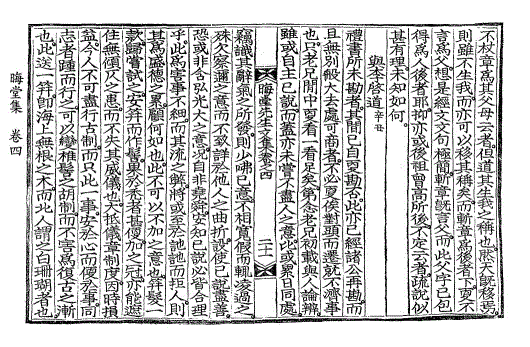 不杖章为其父母云者。但道其生我之称也。然天既移焉。则虽不生我。而亦可以移其称矣。而斩章为后者下。更不言为父。想是经文文句极简。斩章既言父。而此父字已包得为人后者耶。抑亦或后祖曾高所后。不定云者。疏说似甚有理。未知如何。
不杖章为其父母云者。但道其生我之称也。然天既移焉。则虽不生我。而亦可以移其称矣。而斩章为后者下。更不言为父。想是经文文句极简。斩章既言父。而此父字已包得为人后者耶。抑亦或后祖曾高所后。不定云者。疏说似甚有理。未知如何。与李启道(辛丑)
礼书所未勘者。其间已自更勘否。此亦已经诸公再勘。而且无别般大去处可商者。不必更俟对头而迁就不济事也。只老兄閒中更看一看足矣。第念老兄初载与人论辨。虽或自主己说。而盖亦未尝不尽人之意。比或累日同处。窃识其辞气之所发。则少咈己意。不相宽假而辄凌过之。殊欠察迩之意而不致详于他人之曲折。设使己说尽善。恐或非含弘光大之意。况自非尧舜。安知己说必皆合理乎。此为害事不细。而其流之弊。将或至于訑訑而拒人。则其为盛德之累。顾何如也。此不可以不加之意也。笄发一款。归尝试之。安笄而作髻。果于秃者甚便。加之冠。亦能遮住无倾仄之患。而不失其威仪也。大抵仪章制度。因时损益。今人不可尽行古制。而只此一事。安于心而便于事。同志者踵而行之。可以变椎髻之胡制。而不害为复古之渐也。此送一笄。即海上无根之木。而北人谓之白珊瑚者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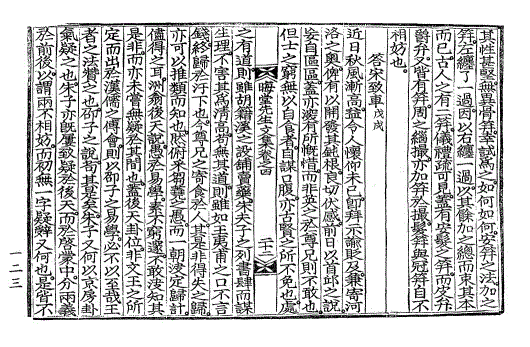 其性甚坚。无异骨笄。幸试为之。如何如何。安笄之法。加之笄。左缠了一过。因以右缠一过。以其馀加之总而束其本而已。古人之有二笄。仪礼疏可见。盖有安发之笄。而皮弁,爵弁。又皆有笄。周之缁撮。亦加笄于撮。发笄与冠笄自不相妨也。
其性甚坚。无异骨笄。幸试为之。如何如何。安笄之法。加之笄。左缠了一过。因以右缠一过。以其馀加之总而束其本而已。古人之有二笄。仪礼疏可见。盖有安发之笄。而皮弁,爵弁。又皆有笄。周之缁撮。亦加笄于撮。发笄与冠笄自不相妨也。答宋致车(戊戌)
近日秋风渐高。益令人怀仰未已。即拜示谕贬及。兼寄河洛之奥。俾有以开发其钝根。良切伏感。前日以首邱之说。妄自区区。盖亦深有所慨惜。而非英之于尊兄则不敢也。但士之穷无以自食者。自谋口腹。亦古贤之所不免也。处之有道。则虽胡籍溪之设铺卖药。朱夫子之列书肆而谋生理。不害其为清高。苟无其道。则虽如王夷甫之口不言钱。终归于污下也。今尊兄之寄食于人。其是非得失之归。亦可以推类而知也。然俯采刍荛之愚。而一朝决定归计。尽得之耳。洲翁后天说。愚于易学。素不穷邃。不敢决知其是非。而亦未尝无疑于其间也。盖后天卦位。非文王之所定而出于汉儒之傅会。则以邵子之易学。必不以至哉王者之法赞之也。邵子之说。苟其是矣。朱子又何以京房卦气疑之也。朱子亦既屡致疑于后天。而于启蒙中。分两义于前后。以谓两不相妨。而初无一字疑辞又何也。是皆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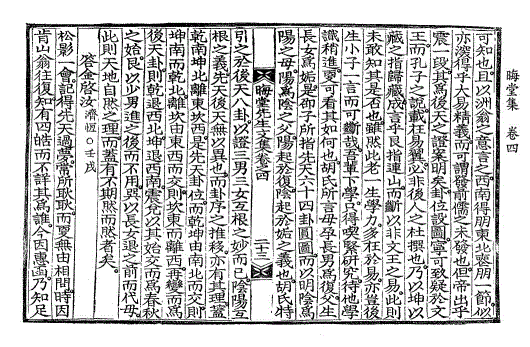 可知也。且以洲翁之意言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一节。似亦深得乎大易精义。而可谓发前儒之未发也。但帝出乎震一段。其为后天之證案明矣。卦位设图。宁可致疑于文王。而孔子之说。载在易翼。必非后人之杜撰也。乃以坤以藏之指归藏。成言乎艮指连山。而断以非文王之易。此则未敢知其是否也。虽然此老一生学力。多在于易。亦岂后生小子一言而可断哉。吾辈下学。只得吃紧研究。待他学识稍进。更可看其如何也。胡氏所言母孕长男为复。父生长女为姤。是邵子所指先天六十四卦圆图。而以明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阳起于复。阴起于姤之义也。胡氏特引之于后天八卦。以證三男三女互根之妙而已。阴阳互根之义。先天后天无以异也。而卦序之推移。亦有其理。盖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是先天卦位。而乾坤由南北而交。则坤南而乾北。离坎由东西而交。则坎东而离西。再变而为后天卦。则乾退西北。坤退西南。震兑以其始交而为春秋之始。艮以少男进之后而不用。巽以长女退之前而代母。此则天地自然之理。而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可知也。且以洲翁之意言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一节。似亦深得乎大易精义。而可谓发前儒之未发也。但帝出乎震一段。其为后天之證案明矣。卦位设图。宁可致疑于文王。而孔子之说。载在易翼。必非后人之杜撰也。乃以坤以藏之指归藏。成言乎艮指连山。而断以非文王之易。此则未敢知其是否也。虽然此老一生学力。多在于易。亦岂后生小子一言而可断哉。吾辈下学。只得吃紧研究。待他学识稍进。更可看其如何也。胡氏所言母孕长男为复。父生长女为姤。是邵子所指先天六十四卦圆图。而以明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阳起于复。阴起于姤之义也。胡氏特引之于后天八卦。以證三男三女互根之妙而已。阴阳互根之义。先天后天无以异也。而卦序之推移。亦有其理。盖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是先天卦位。而乾坤由南北而交。则坤南而乾北。离坎由东西而交。则坎东而离西。再变而为后天卦。则乾退西北。坤退西南。震兑以其始交而为春秋之始。艮以少男进之后而不用。巽以长女退之前而代母。此则天地自然之理。而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答金启汝(济恒○壬戌)
松影一会。记得先天过梦。常所耿耿。而更无由相问。时因肯山翁往复。知有四皓而不详其为谁。今因惠函。乃知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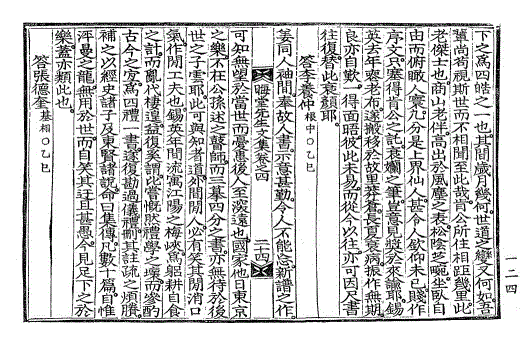 下之为四皓之一也。其间岁月几何。世道之变又何如。吾辈尚苟视斯世而不相闻至此哉。肯公所住相距几里。此老杰士也。商山老伴。高出于风尘之表。松阴芝畹。坐卧自由而俯瞰人寰。九分是上界仙人。甚令人钦仰未已。贱作序文。只塞得肯公之托。衰懒之笔。岂意见奖于来谕耶。锡英去年丧老布。遂搬移于故里莽苍。长夏衰病。振作无期。良亦自叹。一得面晤。彼此未易。而从今以往。亦可因尺书往复。替此衰颜耶。
下之为四皓之一也。其间岁月几何。世道之变又何如。吾辈尚苟视斯世而不相闻至此哉。肯公所住相距几里。此老杰士也。商山老伴。高出于风尘之表。松阴芝畹。坐卧自由而俯瞰人寰。九分是上界仙人。甚令人钦仰未已。贱作序文。只塞得肯公之托。衰懒之笔。岂意见奖于来谕耶。锡英去年丧老布。遂搬移于故里莽苍。长夏衰病。振作无期。良亦自叹。一得面晤。彼此未易。而从今以往。亦可因尺书往复。替此衰颜耶。答李养仲(根中○乙巳)
姜同人袖间。奉故人书。示意甚勤。令人不能忘。新谱之作。可知无望于当世而忧患后人至深远也。国家他日东京之乐。不在公孙述之瞽师。而三摹四分之书。亦无待于后世之子云耶。此可与知者道。外间閒人。必有笑其閒消口气。作閒工夫也。锡英年间流寓江阳之梅峡。为躬耕自食之计。而乱代栖遑。益复奚谓。比尝慨然礼学之坏。而参酌古今之宜。为四礼一书。遂复勘过仪礼。删其注疏之烦剩。补之以经史诸子及东贤诸说。命曰集传。凡数十篇。自惟泙曼之龙。无用于世。而自笑其迂且甚愚。今见足下之于乐。盖亦类此也。
答张德奎(基相○乙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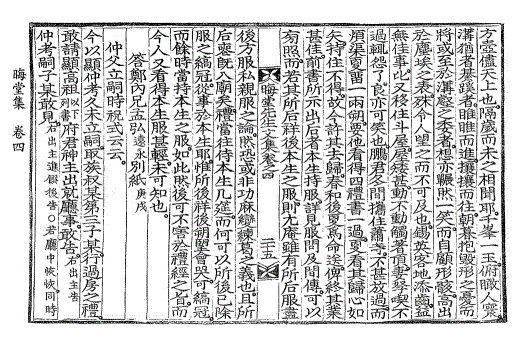 方壶尽天上也。隔岁而未之相闻耶。千峰一玉。俯瞰人寰。沟犹者綦蹊者。睢睢而进。攘攘而往。朝暮抱毁形之忧而将或至于沟壑之委者。想亦冁然一笑。而自顾形骸。高出于尘埃之表。殊令人望之而不可及也。锡英客地添齿。益无佳事。比又移住斗屋。屋矮甚。动不动触著顶。妻孥吃不过辄怨了。良亦可笑也。鹏君冬间携住萧寺。不甚放过。而烦渠更留一两朔。要他看得四礼书一过。更看其归心如矢。持住不得。故今许其去归。春和后更为命送。俾终其业甚佳。前书所示出后者本生持服。详见服问及间传。可以旁照。而若其所后祥后本生之服。则尤庵虽有所后服尽后方服私亲服之论。然恐或非功麻变练葛之义也。且所后丧既入庙矣。礼当往侍本生几筵。而何可以所后已除服之缟冠。从事于本生耶。惟所后祥后朔望会哭。可缟冠。而馀时当持本生之服。如此然后可不害于礼经之旨。而今人又看得本生服甚轻。未可知也。
方壶尽天上也。隔岁而未之相闻耶。千峰一玉。俯瞰人寰。沟犹者綦蹊者。睢睢而进。攘攘而往。朝暮抱毁形之忧而将或至于沟壑之委者。想亦冁然一笑。而自顾形骸。高出于尘埃之表。殊令人望之而不可及也。锡英客地添齿。益无佳事。比又移住斗屋。屋矮甚。动不动触著顶。妻孥吃不过辄怨了。良亦可笑也。鹏君冬间携住萧寺。不甚放过。而烦渠更留一两朔。要他看得四礼书一过。更看其归心如矢。持住不得。故今许其去归。春和后更为命送。俾终其业甚佳。前书所示出后者本生持服。详见服问及间传。可以旁照。而若其所后祥后本生之服。则尤庵虽有所后服尽后方服私亲服之论。然恐或非功麻变练葛之义也。且所后丧既入庙矣。礼当往侍本生几筵。而何可以所后已除服之缟冠。从事于本生耶。惟所后祥后朔望会哭。可缟冠。而馀时当持本生之服。如此然后可不害于礼经之旨。而今人又看得本生服甚轻。未可知也。答郑内兄孟弘(远永)别纸(庚戌)
仲父立嗣时祝式云云。
今以显仲考久未立嗣。取族叔某第三子某。行过房之礼。敢请显高祖(以下列书)府君神主出就厅事。敢告。(右出主告。)
仲考嗣子某敢见。(右出主进馔后告○若厅中恢恢。同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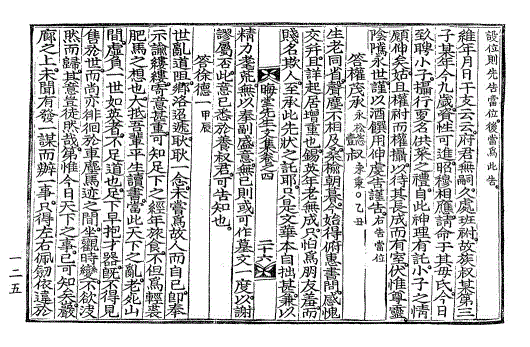 设位则先告当位。后当为此告。)
设位则先告当位。后当为此告。)维年月日干支云云。府君无嗣。久处班祔。故族叔某第三子某年今九岁。资性可进。昭穆相应。请命于其母氏。今日致聘小子。摄行更名供菜之礼。自此神理有托。小子之情愿伸矣。姑且权祔而权摄。以待其长成而有室。伏惟尊灵。阴骘永世。谨以酒馔用伸虔告谨告。(右告当位。)
答权茂承(永松)懿叔(永秉○乙丑)
生老同省。声尘不相及。桑榆朝暮。今始得俯惠书问。感愧交并。且详起居增重也。锡英年老无成。只怕为朋友羞。而贱名欺人。至承此先状之托耶。只是文华本自拙甚。兼以精力耄荒。无以奉副盛意。无已则或可作墓文一度。以谢谬属否。此意已悉于养叔君。可告知也。
答徐德一(甲辰)
世乱道阻。乡洛迢递。耿耿一念。未尝为故人而自已。即奉示谕缕缕。寄意甚重。可知足下之经年旅食。不但为轻裘肥马之想也。大抵吾辈平生读书。当此天下之乱。老死山间。虚负一世如英者。不足道也。足下早抱才器。既不得见售于世。而尚亦徘徊于车尘马迹之间。坐观时变。不欲决然而归。其意岂徒然哉。第惟今日天下之事。已可知矣。岩廊之上。未闻有发一谋而办一事。只得左右佩剑依违于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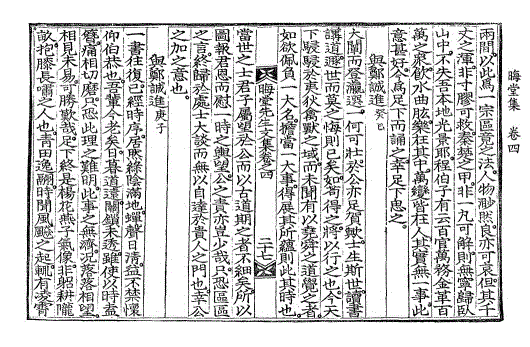 两间。以此为一宗区竟之法。人物渺然。良亦可哀。但其千丈之浑。非寸胶可救。秦楚之甲。非一丸可解。则无宁归卧山中。不失吾本地光景耶。程伯子有云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此意甚好。今为足下而诵之。幸足下思之。
两间。以此为一宗区竟之法。人物渺然。良亦可哀。但其千丈之浑。非寸胶可救。秦楚之甲。非一丸可解。则无宁归卧山中。不失吾本地光景耶。程伯子有云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此意甚好。今为足下而诵之。幸足下思之。与郑诚进(癸巳)
大阐而登瀛选。一何可壮。于公亦足贺欤。士生斯世。读书讲道。遁世而莫之悔则已矣。如苟得之。将以行之也。今天下骎骎于夷狄禽兽之域。而未闻有以尧舜之道觉之者。如欲佩负一大名。担当一大事。得展其所蕴则此其时也。当世之士君子属望于公而以古道期之者不细矣。所以图报君恩而慰一时之舆望。公之责亦岂少哉。只恐区区之言。终归于处士大谈而无以自达于贵人之门也。幸公之加之意也。
与郑诚进(庚子)
一书往复。已经时序。居然绿阴满地。蝉声日清。益不禁怀仰伯恭也。吾辈今老矣。日暮道远。关锁未透。虽使以时盍簪。痛相切磨。只恐此理之难明。此事之无济。况落落相望。相见未易。可胜叹哉。足下终是杨花燕子气像。非躬耕陇亩。抱膝长啸之人也。青田逸翮。时闻风飙之起。辄有凌霄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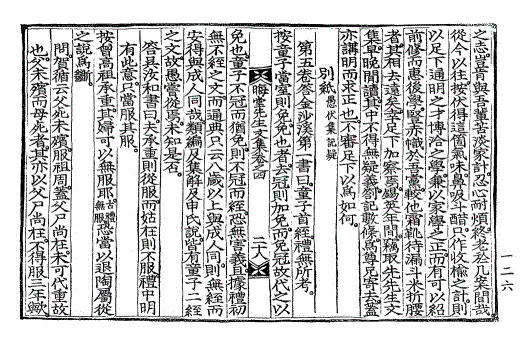 之志。岂肯与吾辈苦淡家计。忍心耐烦。终老于几案间哉。从今以往。按伏得这个气味。鼻吸斗醋。只作收榆之计。则以足下通明之才博洽之学。兼以家学之正。而有可以绍前修而惠后学。竖赤帜于吾党。较他霜靴待漏斗米折腰者。其相去远矣。幸足下加察焉。锡英年间。窃取先先生文集。早晚閒读。其中不得无疑义。劄记数条。为尊兄寄去。盖亦讲明而求正也。不审足下以为如何。
之志。岂肯与吾辈苦淡家计。忍心耐烦。终老于几案间哉。从今以往。按伏得这个气味。鼻吸斗醋。只作收榆之计。则以足下通明之才博洽之学。兼以家学之正。而有可以绍前修而惠后学。竖赤帜于吾党。较他霜靴待漏斗米折腰者。其相去远矣。幸足下加察焉。锡英年间。窃取先先生文集。早晚閒读。其中不得无疑义。劄记数条。为尊兄寄去。盖亦讲明而求正也。不审足下以为如何。别纸(愚伏集记疑)
第五卷答金沙溪第一书曰。童子首绖。礼无所考。
按童子当室则免。免也者。去冠则加免。而免冠故代之以免也。童子不冠而犹免。则不冠而绖。恐无害义。且据礼初无不绖之文。而通典只云八岁以上与成人同。则无绖而安得与成人同哉。类编及集解及申氏说。皆有童子二绖之文。故愚尝从焉。未知是否。
答吴汝和书曰。夫承重则从服。而姑在则不服。礼中明有此意。只当服其服。
按曾高祖承重。其妇可以无服耶。(古礼无服。)恐当以退陶属从之说为断。
问。贺循云父死未殡。服祖周。盖父尸尚在。未可代重故也。父未殡而母死者。其亦以父尸尚在。不得服三年欤。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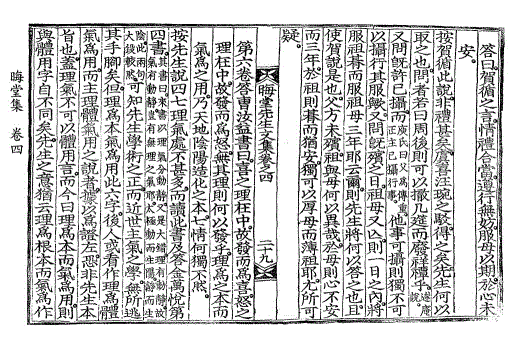 答曰。贺循之言。情礼合当。遵行无妨。服母以期。于心未安。
答曰。贺循之言。情礼合当。遵行无妨。服母以期。于心未安。按贺循此说。非礼甚矣。虞喜汪琬之驳。得之矣。先生何以取之也。问者若曰周后则可以撤几筵而废祥禫乎。(遂庵说。)又问既许已摄。而(庾氏曰父为传重。正主已摄行事。)他事可摄则独不可以摄行其服欤。又问既殡之日。祖母又亡。则一日之内。将服祖期而服祖母三年耶云尔。则先生将何以答之也。且使贺说是也。父方未殡。祖与母何以异哉。于母则心不安而三年。于祖则期而犹安。独可以厚母而薄祖耶。尤所可疑。
第六卷答曹汝益书曰。喜之理在中。故发而为喜。怒之理在中。故发而为怒。无其理则何以发乎。理为之本而气为之用。乃天地阴阳造化之本。七情何独不然。
按先生说四七理气处不甚多。而读此书及答金万悦第四书。(其书曰。来书以理气分动静。又是大错。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岂有无理之气耶。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此两句大段较然。)可知先生学术之正。而近世主气之学。无所逃其手脚矣。但理为本气为用此六字。后人或看作理为体气为用。而主理体气用之说者。据以为證左。恐非先生本旨也。盖理气不可以体用言。而今曰理为本而气为用。则与体用字自不同矣。先生之意犹云理为根本而气为作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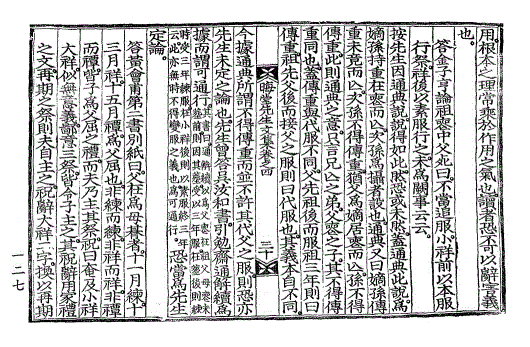 用。根本之理常乘于作用之气也。读者恐不可以辞害义也。
用。根本之理常乘于作用之气也。读者恐不可以辞害义也。答金子亨论祖丧中父死曰。不当追服。小祥前以本服行祭。祥后以素服行之。未为阙事云云。
按先生因通典说。说得如此。然恐或未然。盖通典此说。为嫡孙持重在丧而亡。次孙为摄者设也。通典又曰嫡孙传重未竟而亡。次孙不得传重。犹父为嫡居丧而亡。孙不得传重。此则通典之意。只言兄亡之弟。父丧之子。其不得传重同也。盖传重与代服不同。父先祖后而服祖三年则曰传重。祖先父后而接父之服则曰代服也。其义本自不同。今据通典所谓不得传重而并不许其代父之服。则恐亦先生未定之论也。先生曾答吴汝和书。引勉斋通解续为据而谓可通行。(其书曰。通解续以为父丧在祖父母丧未葬前。则因其葬。受以三年服。在葬后则练时受三年练服。在小祥后则以素服终三年云。此亦无时不得变服之义也。为可通行。)恐当为先生定论。
答黄会甫第二书别纸曰。父在为母期者。十一月练。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为父屈也。非练而练。非祥而祥。非禫而禫。皆子为父屈之礼。而夫乃主其祭。祝曰奄及小祥大祥。似无意义。鄙意三祭。皆令子主之。其祝辞用家礼之文。再期之祭则夫自主之。祝辞大祥二字。换以再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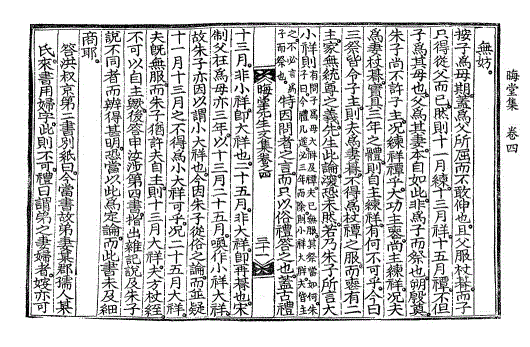 无妨。
无妨。按子为母期。盖为父所屈而不敢伸也。且父服杖期。而子只得从父而已。然则十一月练。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不但子为其母也。父为其妻。本自如此。非为子而祭也。朔殷奠。朱子尚不许子主。况练祥禫乎。大功主丧。尚主练祥。况夫为妻杖期。实具三年之体。则自主练祥。有何不可乎。今曰三祭皆令子主。则夫为妻期。不得为杖禫之服。而丧有二主。家无统尊之义。先生此论。深恐未然。若乃朱子所言大小祥则(有问子为母大祥及禫。夫已无服。其祭当如何。朱子曰。今礼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小祥大祥。夫皆主之。不必言为子而祭也。)特因问者之言。而只以俗礼答之也。盖古礼十三月。非小祥。即大祥也。二十五月。非大祥。即再期也。宋制父在为母亦三年。以十三月二十五月。唤作小祥大祥。故朱子亦因以谓小大祥也。今因朱子从俗之论。而并疑十一月十三月之不得为小大祥可乎。况二十五月大祥。夫既无服。而朱子犹许夫自主。则十三月大祥。夫方杖绖。不可以自主欤。后答申汝涉第四书。指出杂记说及朱子说不同者而辨得甚明。恐当以此为定论。而此书未及细商耶。
答洪叔京第二书别纸曰。今当书故弟妻某郡孺人某氏。来书用妇字。此则不可。礼曰谓弟之妻妇者。嫂亦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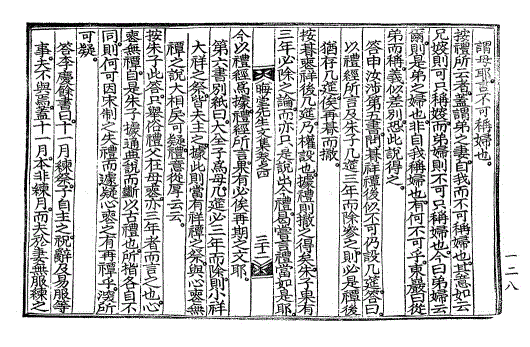 谓母耶。言不可称妇也。
谓母耶。言不可称妇也。按礼所云者。盖谓弟之妻。自我而不可称妇也。其意如云兄嫂则可只称嫂。而弟妇则不可只称妇也。今曰弟妇云尔。则是弟之妇也。非自我称妇也。有何不可乎。东岩曰从弟而称。义似差别。恐此说得之。
答申汝涉第五书。问期祥禫后似不可仍设几筵。答曰。以礼经所言及朱子几筵三年而除参之。则必是禫后犹存几筵。俟再期而撤。
按期丧祥后几筵。乃权设也。据礼则撤之得矣。朱子果有三年必除之论。而亦只是说出今礼。曷尝言礼当如是耶。今以礼经为据。礼经所言。果有必俟再期之文耶。
第六书别纸曰。大全子为母。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据此则当有祥禫之祭。与心丧无禫之说大相戾可疑。礼意从厚云云。
按朱子此答。只举俗礼父在母丧。亦三年者而言之也。心丧无禫。自是朱子据通典说而断以古礼也。所指各自不同。则何可因宋制之失礼而遽疑心丧之有再禫乎。深所可疑。
答李庆馀书曰。十一月练祭。子自主之。祝辞及易服等事。夫不与焉。盖十一月。本非练月。而夫于妻无服练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9H 页
 节故也。十三月之祭则不得已父主之。祝云奄及初期。(自注云以子言则为大祥。而以父言则不可谓大祥。)
节故也。十三月之祭则不得已父主之。祝云奄及初期。(自注云以子言则为大祥。而以父言则不可谓大祥。)按此于前辨已详矣。但练则子主。祥则夫主。此礼尤似可疑。且夫无服练之节云云。于礼有据否。愚谓丧服为妻报以禫杖。有禫则可不服练乎。杂记期之丧。十一月练。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注此为父在为母及为妻。疏夫为妻与母同云云。夫当服练。经文可据。不一而足。先生断以夫不与焉。窃所未晓。况练祭则子主。十三月则夫主。祝云初期。则子为母将有练而无祥耶。夫为妻既无练。又无祥耶。以先生礼学之明。而必无无据之论。抑亦其未定之说耶。百世之下。恨不得一质于玉成讲席而终抱此不决之疑也。
年谱癸亥议礼疏。既已称祖于 宣庙而自称为孙。虽称考于所生而自称为子。未为嫌逼。
按时有三种之议。(朴潜冶直请崇奉。金沙溪引程子濮议。称以叔侄。)而先生此论。最似精当。得其折衷矣。盖 仁庙所处。有异于 宣庙之于德兴。世宗之于兴献。而入承大统。又异于汉哀,宋英。直继父后则称考称子。自无嫌逼。考不加显。子不称孝。期不以杖。则又足以别嫌矣。第有一事难处者。彼主三年之说者每曰前日之称考是矣。则今日之降服非矣。此说似亦然矣。盖初无祢位。而称考称子则只是父子也。焉有不杖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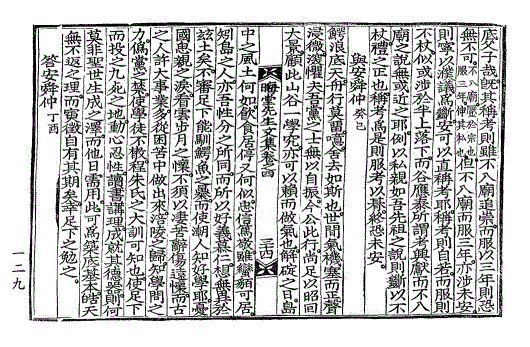 底父子哉。既其称考则虽不入庙追崇。而服以三年则恐无不可。(不入庙。压于宗也。服三年。伸其私也。)但不入庙而服三年。亦涉未安。则宁以濮议为断。安可以直称考耶。称考则自若。而服则不杖。似或涉于半上落下。而谷应泰所谓考兴献而不入庙之说无或近之耶。例以私亲如吾先祖之说则断以不杖。礼之正也。称考为是则服考以期。终恐未安。
底父子哉。既其称考则虽不入庙追崇。而服以三年则恐无不可。(不入庙。压于宗也。服三年。伸其私也。)但不入庙而服三年。亦涉未安。则宁以濮议为断。安可以直称考耶。称考则自若。而服则不杖。似或涉于半上落下。而谷应泰所谓考兴献而不入庙之说无或近之耶。例以私亲如吾先祖之说则断以不杖。礼之正也。称考为是则服考以期。终恐未安。与安舜仲(癸巳)
鳄浪底天。舟行莫留。噫。舍去如斯也。世间气机塞而正声浸微。深惧夫吾党之士无以自振。今公此行。尚足以昭回大景。顾此山谷一学究。亦可以赖而做气也。解碇之日。岛中之风土何如。饮食居停又何似。忠信笃敬。虽蛮貊可居。矧岛之人。亦吾性分之所同。而所以好义慕仁。想无异于玆土矣。不审足下能驯鳄鱼之㬥。而使潮人知好学耶。忧国思亲之泪。看云步月之怀。不须以凄苦辞伤远怀。而古之人许大事业。多从困苦中做出来。涪陵之归。知学问之力。伪党之禁。使学徒不散。程朱氏之大训可知也。使足下而投之九死之地。动心忍性。读书讲理。成就其德器。则何莫非圣世生成之泽。而他日需用。此可为筑底基本。皓天无不返之理。而寅徵自有其期矣。幸足下之勉之。
答安舜仲(丁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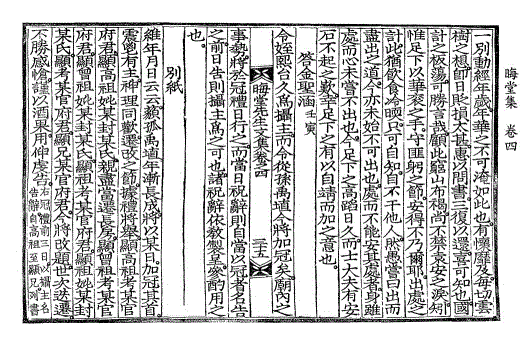 一别动经年岁。年华之不可淹如此也。有怀靡及。每切云树之想。即日贬损太甚。惠以问书。三复以还。喜可知也。国计之板荡。可胜言哉。顾此穷山布褐。尚不禁袁安之泪。矧惟足下以华衮之手。守匪躬之节。安得不乃尔耶。出处之计。此犹饮食冷暖。只可自知。自不干他人。然愚尝曰出而尽出之道。今亦未始不可出也。处而不能安其处者。身虽处而心未尝不出也。今足下之高蹈日久。而士大夫有安石不起之叹。幸足下之有以自靖而加之意也。
一别动经年岁。年华之不可淹如此也。有怀靡及。每切云树之想。即日贬损太甚。惠以问书。三复以还。喜可知也。国计之板荡。可胜言哉。顾此穷山布褐。尚不禁袁安之泪。矧惟足下以华衮之手。守匪躬之节。安得不乃尔耶。出处之计。此犹饮食冷暖。只可自知。自不干他人。然愚尝曰出而尽出之道。今亦未始不可出也。处而不能安其处者。身虽处而心未尝不出也。今足下之高蹈日久。而士大夫有安石不起之叹。幸足下之有以自靖而加之意也。答金圣涵(壬寅)
令侄熙台久为摄主。而令从孙禹埴今将加冠矣。庙内之事势。将于冠礼日行之。而当日祝辞则自当以冠者名告之。前日告则摄主为之可也。诸祝辞依教制呈。参酌用之也。
别纸
维年月日云云。藐孤禹埴。年渐长成。将以某日。加冠其首。震鬯有主。神理同欢。迁改之节。据礼将举。显高祖考某官府君。显高祖妣某封某氏。亲尽当迁长房。显曾祖考某官府君。显曾祖妣某封某氏。显祖考某官府君。显祖妣某封某氏。显考某官府君。显兄某官府君。今将改题。世次迭迁。不胜感怆。谨以酒果。用伸虔告。(右冠礼前三日。以摄主名告辞。自高祖至显兄。列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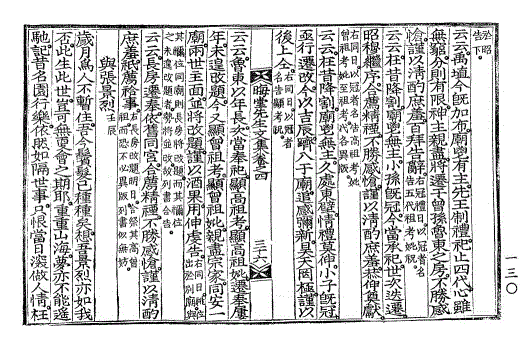 于昭告下。)
于昭告下。)云云。禹埴今既加布。庙鬯有主。先王制礼。祀止四代。心虽无穷。分则有限。神主亲尽。将迁于曾孙鲁东之房。不胜感怆。谨以清酌庶羞。百拜告辞。(右冠礼日。以冠者名告五代祖考妣祝。)
云云。在昔降割。庙鬯无主。小孙既冠。今当承祀。世次迭迁。昭穆继序。合荐精禋。不胜感怆。谨以清酌庶羞。恭伸奠献。(右同日。以冠者名告高祖考妣曾祖考妣至祖考。代各异版。)
云云。在昔降割。庙鬯无主。久处东壁。情礼莫伸。小子既冠。亟行迁改。今以吉辰。跻入于庙。追感弥新。昊天罔极。谨以后上仝。(右同日。以冠者名告显考祝。)
云云。鲁东以年长。次当奉祀。显高祖考。显高祖妣。迁奉屡年。未遑改题。今又显曾祖考。显曾祖妣。亲尽宗家。同安一庙。两世主面。并将改题。谨以酒果。用伸虔告。(右同日。祧位出于别庙。与其祢位同庙则长房将改题。而其祢位之未遑改题者。势将并改。故列书合告。)
云云。长房迁奉。依旧同宫。合荐精禋。不胜感怆。谨以清酌庶羞。祇荐祫事。(右长房改题明日。合祭其高曾祖。而恐不必异版。列书似无妨。)
与张景烈(壬辰)
岁月为人不暂住。吾今鬓发已种种矣。想吾景烈亦如我否。此生此世。岂可无更会之期耶。重重山海。梦亦不能遥驰。记昔名园行乐。依然如隔世事。只恨当日深做人情。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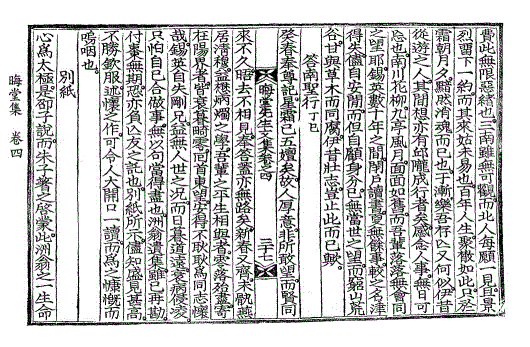 费此无限恶绪也。三南虽无可观。而北人每愿一见。且景烈留下一约。而其来姑未易也。百年人生。聚散如此。只于霜朝月夕。黯然消魂而已也。于渐,乐吾存亡又何似。伊昔从游之人。其间想亦有邱陇成行者矣。感念人事。无日可忘也。南川花柳。九亭风月。面面如旧。而吾辈落落无会同之望耶。锡英数十年之间。闭户读书。更无馀事。较之名津得失。尽自安閒。而但自顾身分。已无当世之望。而穷山荒谷。甘与草木而同腐。伊昔壮志。岂止此而已欤。
费此无限恶绪也。三南虽无可观。而北人每愿一见。且景烈留下一约。而其来姑未易也。百年人生。聚散如此。只于霜朝月夕。黯然消魂而已也。于渐,乐吾存亡又何似。伊昔从游之人。其间想亦有邱陇成行者矣。感念人事。无日可忘也。南川花柳。九亭风月。面面如旧。而吾辈落落无会同之望耶。锡英数十年之间。闭户读书。更无馀事。较之名津得失。尽自安閒。而但自顾身分。已无当世之望。而穷山荒谷。甘与草木而同腐。伊昔壮志。岂止此而已欤。答南圣行(丁巳)
癸春奉尊记。星霜已五嬗矣。故人厚意。非所敢望。而贤同来不久。晤去不相见。奉答盖亦无路矣。新春又齐。未骫燕居清穆。益懋炳烛之学。吾辈之平生相与者。零落殆尽。寄在阳界者。皆衰暮畸零。回首东望。安得不耿耿为同志怀哉。锡英自失刚兄。益无人世之况。而日暮道远。衰病侵凌。只怕自己合做事。无以句当得尽也。洲翁遗集。虽已再勘。付枣无期。恐亦负亡友之托也。别纸所示。尽知盛见甚高。不胜钦服。述怀之作。可令人大开口一读。而为之慷慨而呜咽也。
别纸
心为太极。是邵子说。而朱子著之启蒙。此洲翁之一生命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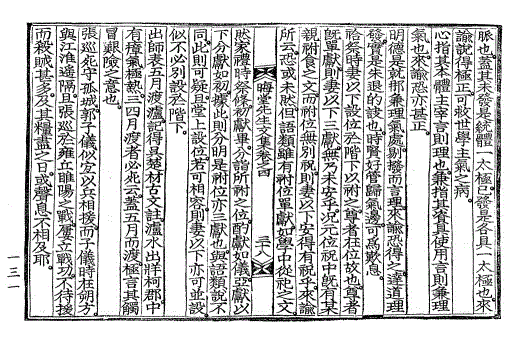 脉也。盖其未发是统体一太极。已发是各具一太极也。来谕说得极正。可救世学主气之病。
脉也。盖其未发是统体一太极。已发是各具一太极也。来谕说得极正。可救世学主气之病。心指其本体主宰言则理也。兼指其资具使用言则兼理气也。来谕恐亦甚正。
明德是就那兼理气处。剔拨而言理。来谕恐得之。达道理发。实是朱退的诀也。时贤好管归气边。可为叹息。
祫祭时妻以下设位于阶下以祔之。尊者在位故也。尊者既单献。则妻以下三献。无乃未安乎。况元位祝中既有某亲祔食之文。而祔位无别祝。则妻以下安得有祝乎。来谕所云。恐或未然。但语类虽有祔位单献。如学中从祀之文。然家礼时祭条。初献毕。分诣所祔之位。酌献如仪。亚献以下分献如初。据此则分明是祔位亦三献也。与语类说不同。此则可疑。且堂上设位。若可相容。则妻以下亦可并设。似不必别设于阶下。
出师表五月渡泸。记得吴楚材古文注。泸水出牂柯郡。中有瘴气极热。三四月渡者必死云。盖五月而渡。极言其触冒艰险之意也。
张巡死守孤城。郭子仪似宜以兵相援。而子仪时在朔方。与江淮遥隔。且张巡于雍丘睢阳之战。屡立战功。不待援而杀贼甚多。及其粮尽之日。或声息不相及耶。
答李弼瑞(直铉○丁巳)
十年知面。一朝许心。一札心画。又替此面。此区区之荣也。第惟锡英平生寡谐于人。而还被尊兄之记录。以其愚甚。有似直谅也。今奉来谕。若将有过而惮改。无乃是善戏之辞欤。有人于此。人有遗药。许之以受。而还道吾自无病。无以尔药也。盖有病则可受。无病则勿许可也。充类言之。大兄之言。无或近之欤。吾辈馀生。交修共济。庶无愧于圣贤之训。不亦可乎。顾瞻南服。望津有足下。惟足下自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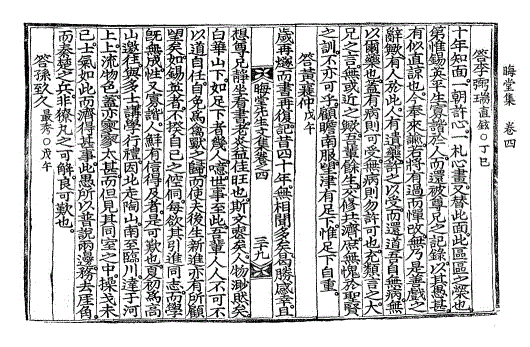 答黄襄仲(戊午)
答黄襄仲(戊午)岁再燧而书再复。记昔四十年。无相闻多矣。曷胜感幸。且想尊兄静坐看书。老炎益佳旺也。斯文丧矣。人物渺然矣。白华山下。如足下者几人。噫。世事至此。吾辈人人不可不以道自任。自免为禽兽之归。而使夫后生新进亦有所顾望矣。如锡英者。不揆自己之倥侗。每欲其引进同志。而学既无成。性又寡谐。人鲜有信得及者。是可叹也。夏初为高山邀往。与多士讲学行礼。因北走陶山。南至临川。达于河上。上流物色。盖亦寥寥太甚。而但见其同室之中。操戈未已。士气如此而济得甚事。此愚所以普说两边。务去厓角。而秦楚之兵。非獠丸之可解。良可叹也。
答孙致久(最秀○戊午)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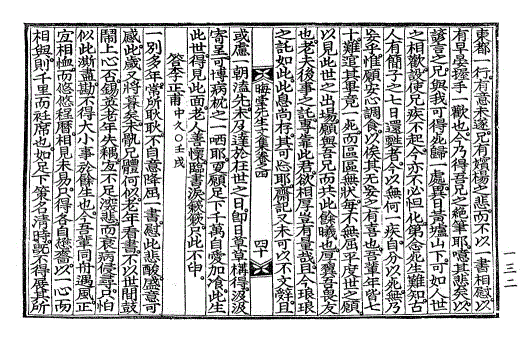 东都一行。有意未遂。兄有嫔杨之悲。而不以一书相慰。以有早晏握手一欢也。今乃得吾兄之绝笔耶。噫其悲矣。以谚言之。兄与我可得死归一处。异日黄垆山下。可如人世之相欢。设使兄疾不起。今亦不必怛化。第念死生难知。古人有简子之七日还苏者。今以无何一疾。自分以死。无乃妄乎。惟愿安心调食。以俟其无妄之有喜也。吾辈年皆七十。难逭其毕竟一死。而区区无状。每不无屈平度世之愿。以见此世之出场。愿与吾兄而共此馀曦也。厚翼吾畏友也。老夫后事之托。专靠此君。欲相厚岂有量哉。且今琅琅之托如此。此息尚存。其可忘耶。斋记又未可以不文辞。且或虑一朝溘先。未及达于在世之日。即日草草构得。汲汲寄呈。可博病枕之一哂耶。更愿足下千万自爱加餐。此生此世。得见此面。老人善怀。临书泪簌簌。只此不申。
东都一行。有意未遂。兄有嫔杨之悲。而不以一书相慰。以有早晏握手一欢也。今乃得吾兄之绝笔耶。噫其悲矣。以谚言之。兄与我可得死归一处。异日黄垆山下。可如人世之相欢。设使兄疾不起。今亦不必怛化。第念死生难知。古人有简子之七日还苏者。今以无何一疾。自分以死。无乃妄乎。惟愿安心调食。以俟其无妄之有喜也。吾辈年皆七十。难逭其毕竟一死。而区区无状。每不无屈平度世之愿。以见此世之出场。愿与吾兄而共此馀曦也。厚翼吾畏友也。老夫后事之托。专靠此君。欲相厚岂有量哉。且今琅琅之托如此。此息尚存。其可忘耶。斋记又未可以不文辞。且或虑一朝溘先。未及达于在世之日。即日草草构得。汲汲寄呈。可博病枕之一哂耶。更愿足下千万自爱加餐。此生此世。得见此面。老人善怀。临书泪簌簌。只此不申。答李正甫(中久○壬戌)
一别多年。常所耿耿。不自意降屈一书。慰此悲酸。盛意可感。此岁又将暮矣。未骫兄体何似。老年看书。不以世间鼓闹上心否。锡英老年失耦。宜不足深悲。而衰病侵寻。只怕似此澌尽。勘不得大小事于馀生也。今吾辈同舟遇风。正宜相恤。而悠悠程历。相见未易。只得各自懋啬。以一心而相与。则千里而衽席也。如足下策名清时。既不得展其所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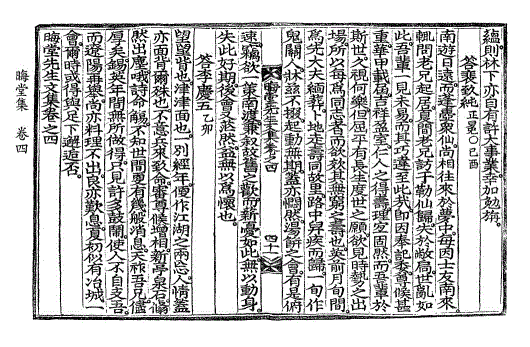 蕴。则林下亦自有许大事业。幸加勉旃。
蕴。则林下亦自有许大事业。幸加勉旃。答裴致纯(正冕○己酉)
南游日远。而蓬壶众仙。尚相往来于梦中。每因士友南来。辄问老兄起居。夏间老兄访于勒仙归。失于敝扃。世乱如此。吾辈一见未易。而其巧违至此哉。即因奉记委。尊候甚重。华甲载届。吉祥盈室。仁人之得寿。理宜固然。而吾辈于斯世。久视何乐。但屈平有长生度世之愿。欲见时势之出场。所以每为同志者而欲效其无穷之寿也。英前月旬间。为先大夫缅葬。卜地走寿同故里。路中舁疾而归。一旬作鬼关人。床玆不掇。起动无期。盖亦悯然。汤饼之会。有是俯速。窃欲一策南渡。兼叙故旧之欢。而薪忧如此。无以动身。失此好期。后会又茫然。益无以为怀也。
答李庆五(乙卯)
望望背也。津津面也。一别经年。便作江湖之两忘。人情盖亦面背尔殊也。不意兵来致命。审尊候增相。新亭泉石。翛然出尘。哦诗命觞。不知世间更有几般消息。天祚吾兄。尽厚矣。锡英年间无所做得。只见许多鼓闹。使人不自支吾。而辽阳再举。尚亦料理不出。良亦叹息。夏初似有冶城一会。尔时或得与足下邂逅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