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书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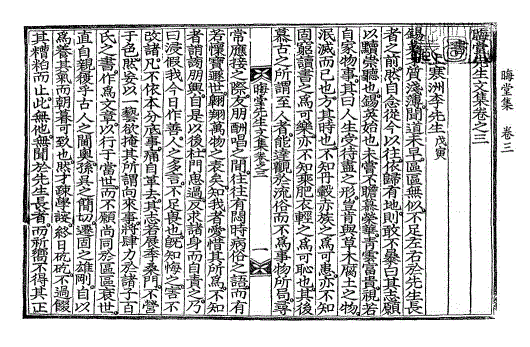 上寒洲李先生(戊寅)
上寒洲李先生(戊寅)锡英才质浅薄。闻道未早。区区无似。不足左右于先生长者之前。然自念从今以往。依归有地。则敢不㬥白其志愿以黩崇听也。锡英始也未尝不瞻慕荣华。青云富贵。视若自家物事。其曰人生受待尽之形。岂肯与草木腐土之物。泯灭而已也。方其时也。不知丹毂赤族之为可患。亦不知固穷读书之为可乐。亦不知乘肥衣轻之为可耻也。其后慕古之所谓至人者。能达观于流俗而不为事物所局。寻常应接之际。友朋酬唱之间。往往有闷时病俗之语。而有若怀宝遁世。翱翔万物之表矣。知我者爱惜其所为。不知者诮谤朋兴。自是以后。杜门思过。反求诸身而自责之。乃曰浸假我今日作善。人之多言。不足畏也。既知悔之。害不改诸。凡不依本分底事。痛自革去。其志若展季桑门。不营于色。然妄以一艺欲掩其所谓向来事。将肆力于诸子百氏之书。作为文章。以行于当世。而不愿尚同于区区衰世。直自亲履乎古人之阃奥。孙吴之简切。迁固之雄刚。自以为养其气而朝暮可致也。然才疏学謏。终日矻矻。不过啜其糟粕而止。此无他。无闻于先生长者。而祈向不得其正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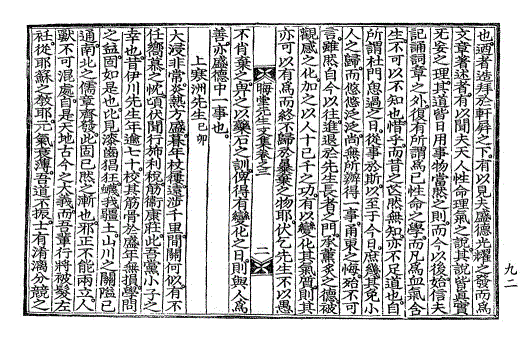 也。乃者造拜于轩屏之下。有以见夫盛德光耀之发而为文章著述者。有以闻夫天人性命理气之说。其说皆真实无妄之理。其道皆日用事物当然之则。而今以后。始信夫记诵词章之外。复有所谓为己性命之学。而凡为血气含生。不可以不知也。惜乎。而昔之芒然无知。亦不足道也。自所谓杜门思过之日。从事于斯。以至于今日。庶几其免小人之归。而悠悠泛泛。尚无所办得一事。甬东之悔。殆不可言。虽然自今以往。进退于先生长者之门。承薰炙之德。被观感之化。加之以人十己千之功。有以变化其气质。则其亦可以有为而终不归于㬥弃之物耶。伏乞先生不以愚不肖弃之。畀之以药石之训。俾得有变化之日。则与人为善。亦盛德中一事也。
也。乃者造拜于轩屏之下。有以见夫盛德光耀之发而为文章著述者。有以闻夫天人性命理气之说。其说皆真实无妄之理。其道皆日用事物当然之则。而今以后。始信夫记诵词章之外。复有所谓为己性命之学。而凡为血气含生。不可以不知也。惜乎。而昔之芒然无知。亦不足道也。自所谓杜门思过之日。从事于斯。以至于今日。庶几其免小人之归。而悠悠泛泛。尚无所办得一事。甬东之悔。殆不可言。虽然自今以往。进退于先生长者之门。承薰炙之德。被观感之化。加之以人十己千之功。有以变化其气质。则其亦可以有为而终不归于㬥弃之物耶。伏乞先生不以愚不肖弃之。畀之以药石之训。俾得有变化之日。则与人为善。亦盛德中一事也。上寒洲先生(己卯)
大浸非常。炎热方盛。暮年杖屦。远涉千里。间关何似。有不任向慕之忱。顷伏闻行旆利税。筋卫康庄。此吾党小子之幸也。昔伊川先生年逾七十。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学问之益。固如是也。比见漆齿猖狂。蔑我疆土。山川之关隘已通。南北之儒章齐发。此固已然之渐也。邪正不能两立。人兽不可混处。自是天地古今之大义。而吾辈行将被发左衽。从耶苏之教耶。元气衰薄。吾道不振。士有淆漓分竞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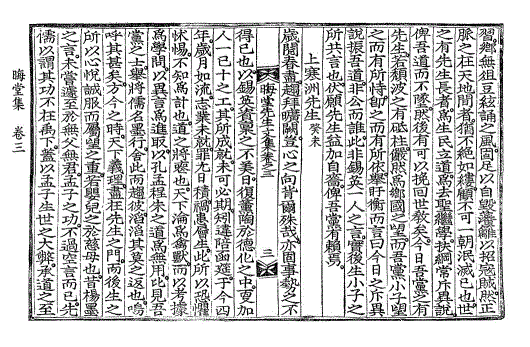 习。乡无俎豆弦诵之风。固足以自毁藩篱以招寇贼。然正脉之在天地间者。犹不绝如缕。顾不可一朝泯灭已也。世之有先生长者。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学。扶纲常斥异说。俾吾道而不坠。然后有可以挽回世教矣。今日吾党之有先生。若颓波之有砥柱。俨然为乡国之望。而吾党小子望之而有所恃。即之而有所依。举盱衡而言曰今日之斥异说振吾道。非公而谁。此非锡英一人之言。实后生小子之所共言也。伏愿先生益加自啬。俾吾党有赖焉。
习。乡无俎豆弦诵之风。固足以自毁藩篱以招寇贼。然正脉之在天地间者。犹不绝如缕。顾不可一朝泯灭已也。世之有先生长者。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学。扶纲常斥异说。俾吾道而不坠。然后有可以挽回世教矣。今日吾党之有先生。若颓波之有砥柱。俨然为乡国之望。而吾党小子望之而有所恃。即之而有所依。举盱衡而言曰今日之斥异说振吾道。非公而谁。此非锡英一人之言。实后生小子之所共言也。伏愿先生益加自啬。俾吾党有赖焉。上寒洲先生(癸未)
岁阅春尽。趋拜旷阙。岂心之向背尔殊哉。亦固事势之不得已也。以锡英资禀之不美。日复薰陶于德化之中。更加人一己十之工。其所成就。未可必期。矧违陪函筵。于今四年。岁月如流。志业未就。罪尤日积。祸患层生。此所以恐惧怵惕。不知为计也。道之将丧也。天下沦为禽兽。而以考据为学问。以异言为进取。以孔孟程朱之道为无用。比见吾党之士。举将儒名墨行。舍此而趋彼。滔滔其莫之返也。呜呼其甚矣。方今之时。天下义理。尽在先生之门。而后生之所以心悦诚服而属望之重。若婴儿之于慈母也。昔杨墨之言。未尝遽至于无父无君。孟子之功。不过空言而已。先儒以谓其功不在禹下。盖以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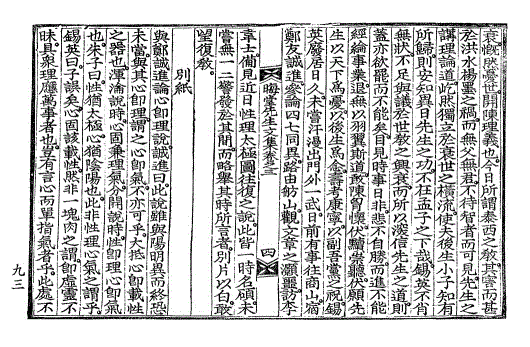 衰。慨然忧世。开陈理义也。今日所谓泰西之教。其害而甚于洪水杨墨之祸。而无父无君。不待智者而可见。先生之讲理论道。屹然独立于衰世之横流。使夫后生小子知有所归。则安知异日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哉。锡英不肖无状。不足与议于世教之兴衰。而所以深信先生之道。则盖亦欲罢而不能矣。目见时事日非。悲不自胜。而进不能经纶事业。退无以羽翼斯道。敢陈胸怀。伏黩崇听。伏愿先生以天下为忧。以后生为念。寿考康宁。以副吾党之祝。锡英废居日久。未尝汗漫出门外一武。日前有事往商山。宿郑友诚进。参论四七同异。路由舫山。观文章之灏噩。访李韦士。备见近日性理太极图往复之说。此皆一时名硕。未尝无一二警发于其间。而略举其时所言者。别片以白。敢望复教。
衰。慨然忧世。开陈理义也。今日所谓泰西之教。其害而甚于洪水杨墨之祸。而无父无君。不待智者而可见。先生之讲理论道。屹然独立于衰世之横流。使夫后生小子知有所归。则安知异日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哉。锡英不肖无状。不足与议于世教之兴衰。而所以深信先生之道。则盖亦欲罢而不能矣。目见时事日非。悲不自胜。而进不能经纶事业。退无以羽翼斯道。敢陈胸怀。伏黩崇听。伏愿先生以天下为忧。以后生为念。寿考康宁。以副吾党之祝。锡英废居日久。未尝汗漫出门外一武。日前有事往商山。宿郑友诚进。参论四七同异。路由舫山。观文章之灏噩。访李韦士。备见近日性理太极图往复之说。此皆一时名硕。未尝无一二警发于其间。而略举其时所言者。别片以白。敢望复教。别纸
与郑诚进论心即理说。诚进曰。此说虽与阳明异而终恐未当。与其心即理。谓之心即气。不亦可乎。大抵心即载性之器也。浑沦说时。心固兼理气。分开说时。性即理心即气也。朱子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也。此非性理心气之谓乎。锡英曰。子误矣。心固该载性。然非一块肉之谓。即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者也。岂有言心而单指气者乎。此处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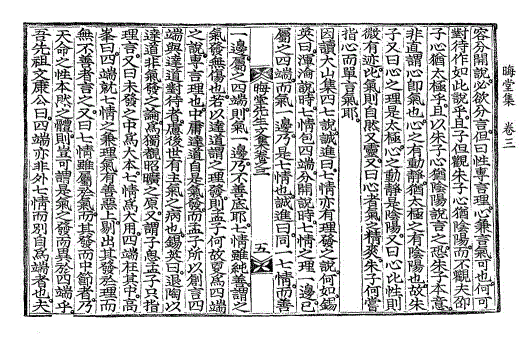 容分开说。必欲分言。但曰性专言理。心兼言气可也。何可对待作如此说乎。且子但观朱子心犹阴阳。而不观夫邵子心犹太极乎。且以朱子心犹阴阳说言之。恐朱子本意。非直谓心即气也。心之有动静。犹太极之有阴阳也。故朱子又曰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又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又曰心者气之精爽。朱子何尝指心而单言气耶。
容分开说。必欲分言。但曰性专言理。心兼言气可也。何可对待作如此说乎。且子但观朱子心犹阴阳。而不观夫邵子心犹太极乎。且以朱子心犹阴阳说言之。恐朱子本意。非直谓心即气也。心之有动静。犹太极之有阴阳也。故朱子又曰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又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又曰心者气之精爽。朱子何尝指心而单言气耶。因读大山集四七说。诚进曰。七情亦有理发之说。何如。锡英曰。浑沦说时。七情包四端。分开说时。七情之理一边。已属之四端。而气一边。乃是七情也。诚进曰。同一七情。而善一边。属之四端。则气一边。乃不善底耶。七情虽纯善。谓之气发无伤也。若以达道谓之理发。则孟子何故更为四端之说。专言理也。中庸达道自是气发。而孟子所以创言四端与达道对待者。虑后世有主气之病也。锡英曰。退陶以达道非气发之论。为独睹昭旷之原。又谓子思孟子只指理言。又曰未发之中为大本。七情为大用。四端在其中。高峰曰。四端就七情之兼理气有善恶上。剔出其发于理而无不善者言之。又曰七情虽属于气。而其发而中节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体。则岂可谓是气之发而异于四端乎。吾先祖文康公曰。四端亦非外七情而别自为端者也。夫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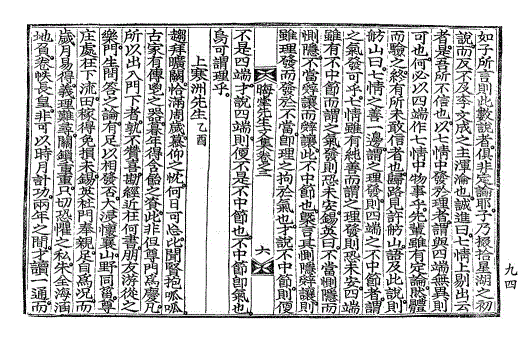 如子所言则此数说者。俱非定论耶。子乃掇拾星湖之初说。而反不及李文成之主浑沦也。诚进曰。七情上剔出云者。是吾所不信也。以七情中发于理者。谓与四端无异则可也。何必以四端作七情中物事乎。先辈虽有定论。然体而验之。终有所未敢信者也。归路见许舫山。语及此说。则舫山曰。七情之善一边。谓之理发。则四端之不中节者。谓之气发可乎。七情虽有纯善而谓之理发则恐未安。四端虽有不中节而谓之气发则恐未安。锡英曰。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辞让而辞让。此不中节也。槩言其恻隐辞让。则虽理发而发于不当。即理之拘于气也。才说不中节。则便不是四端。才说四端。则便不是不中节也。不中节即气也。乌可谓理乎。
如子所言则此数说者。俱非定论耶。子乃掇拾星湖之初说。而反不及李文成之主浑沦也。诚进曰。七情上剔出云者。是吾所不信也。以七情中发于理者。谓与四端无异则可也。何必以四端作七情中物事乎。先辈虽有定论。然体而验之。终有所未敢信者也。归路见许舫山。语及此说。则舫山曰。七情之善一边。谓之理发。则四端之不中节者。谓之气发可乎。七情虽有纯善而谓之理发则恐未安。四端虽有不中节而谓之气发则恐未安。锡英曰。不当恻隐而恻隐。不当辞让而辞让。此不中节也。槩言其恻隐辞让。则虽理发而发于不当。即理之拘于气也。才说不中节。则便不是四端。才说四端。则便不是不中节也。不中节即气也。乌可谓理乎。上寒洲先生(乙酉)
趋拜旷阙。恰满周岁。慕仰之忱。何日可忘。比闻贤抱呱呱。古家有传鬯之器。暮年得含饴之资。此非但尊门为庆。凡所以出入门下者。孰不赞喜。勘经近在何书。朋友游从之乐。门生问答之论。有足以相发否。大浸怀襄。山野同菑。尊庄处在下流。田稼得免损未。锡英杜门奉亲。足自为况。而岁月易得。义理难寻。关锁重重。只切恐惧之私。朱全海涵地负。卷帙长皇。非可以时月计功。两年之间。才读一通。而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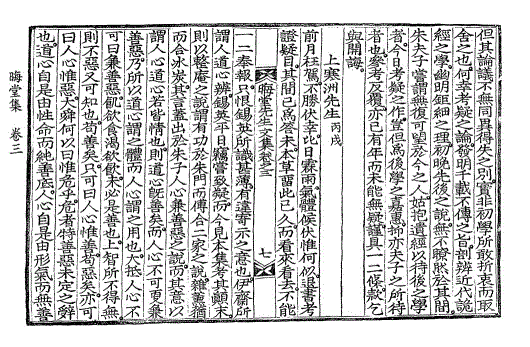 但其论议不无同异得失之别。实非初学所敢折衷而取舍之也。何幸考疑之论。发明千载不传之旨。剖辨近代诡经之学。幽明钜细之理。初晚先后之说。无不瞭然于其间。朱夫子尝谓无复可望于今之人。姑抱遗经以待后之学者。今日考疑之作。岂但为后学之嘉惠。抑亦夫子之所待者也。参考反覆。亦已有年而未能无疑。谨具一二条。款乞与开诲。
但其论议不无同异得失之别。实非初学所敢折衷而取舍之也。何幸考疑之论。发明千载不传之旨。剖辨近代诡经之学。幽明钜细之理。初晚先后之说。无不瞭然于其间。朱夫子尝谓无复可望于今之人。姑抱遗经以待后之学者。今日考疑之作。岂但为后学之嘉惠。抑亦夫子之所待者也。参考反覆。亦已有年而未能无疑。谨具一二条。款乞与开诲。上寒洲先生(丙戌)
前月枉驾。不胜伏幸。比日霖雨。气体候伏惟何似。退书考證疑目。其间已为答未。本草留此已久。而看来看去。不能一二奉报。只恨锡英所识甚薄。有违寄示之意也。伊斋所谓人道心辨。锡英平日窃尝致疑。而今见本集。考其颠末。则以整庵之说谓有功于朱门而傅合二家之说。杂薰莸而合冰炭。其言盖出于朱子人心兼善恶之说。而其意以谓人心道心若皆情也。则道心既善矣。而人心不可更兼善恶。乃所以道心谓之体而人心谓之用也。大抵人心不可曰兼善恶。饥欲食渴欲饮。未必是善也。上智所不得无。则不恶又可知也。苟善矣。只可曰人心惟善。苟恶矣。亦可曰人心惟恶。大舜何以曰惟危乎。危者特善恶未定之辞也。道心自是由性命而纯善底。人心自是由形气而无善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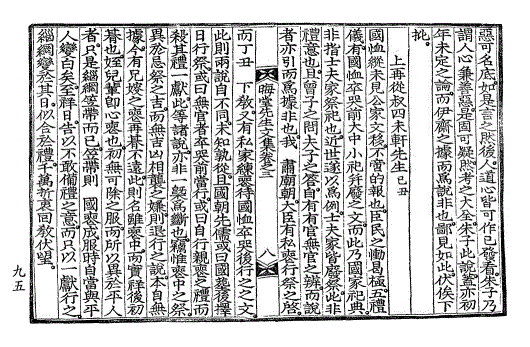 恶可名底。如是言之然后。人道心皆可作已发看。朱子乃谓人心兼善恶。是固可疑。然考之大全。朱子此说。盖亦初年未定之论。而伊斋之据而为说非也。鄙见如此。伏俟下批。
恶可名底。如是言之然后。人道心皆可作已发看。朱子乃谓人心兼善恶。是固可疑。然考之大全。朱子此说。盖亦初年未定之论。而伊斋之据而为说非也。鄙见如此。伏俟下批。上再从叔四未轩先生(己丑)
国恤纵未见公家文移。不啻的报也。臣民之恸曷极。五礼仪。有国恤卒哭前大中小祀并废之文。而此乃国家祀典。非指士夫家祭祀也。近世遂以为例。士夫家皆废祭。此非礼意也。且曾子之问夫子之答。自有有官无官之辨。而说者亦引而为据非也。我 肃庙朝。大臣有私丧行祭之启。而丁丑 下教。又有私家练丧待国恤卒哭后行之之文。此则两说自不同。未知孰从。且国朝先儒或曰国葬后择日行祭。或曰无官者卒哭前当行。或曰自行亲丧之礼而杀其礼一献。此等诸说。亦非一槩为断也。窃惟丧中之祭。异于忌祭之吉。而无吉凶相袭之嫌。则退行之说。本自无据。今有兄嫂之丧再期不远。此则名虽丧中。而实祥后初期也。侄儿辈即心丧也。初无可除之服。而所以异于平人者。只是缁网笠带而已。笠带则 国丧成服时自当与平人变白矣。至祥日。告以不敢备礼之意。而只以一献行之。缁网变于其日。似合于礼。千万折衷回教伏望。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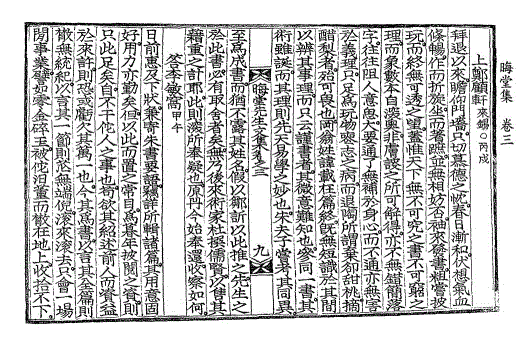 上郑顾轩(来锡○丙戌)
上郑顾轩(来锡○丙戌)拜退以来。瞻仰门墙。只切慕德之忱。春日渐和。伏想气血条畅。作而折旋。坐而著蹠。并无相妨否。袖来发书。粗尝披玩。而终无可透之望。盖惟天下无不可究之书不可穷之理。而象数本自深奥。非肤謏之所可解得。亦不无错简落字。往往阻人意思。大要通了无补于身心。而不通亦无害于义理。只足为玩物丧志之病。而退陶所谓弃却甜桃。摘醋梨者。殆可畏也。冈翁姓讳载在篇终。既无短识于其间以辨其事理。而只云谨书者。其微意难知也。参同一书。其术虽诞。而其理则先天易学之妙也。朱夫子尝考其同异。至为成书。而犹不露其姓名。假以邹䜣以此推之。先生之于此书。必有取舍者矣。无乃后来术家杜撰儒贤。以售其藉重之计耶。此则深所奉疑也。原册今始奉还。收察如何。
答李敏窝(甲午)
日前惠及下状。兼寄朱书要语。窃详所辑诸篇。其用意固好。用力亦勤矣。但以此而置之常目。为暮年披阅之资。则只此足矣。自不干佗人之事也。苟欲其绍述前人而资益于来许。则恐或亏欠其万一也。今其为书。以言其全篇则散无统纪。以言其一节则茫无端倪。滚来滚去。只会一场閒事业。譬如零金碎玉。被佗汩董而散在地上。收拾不下。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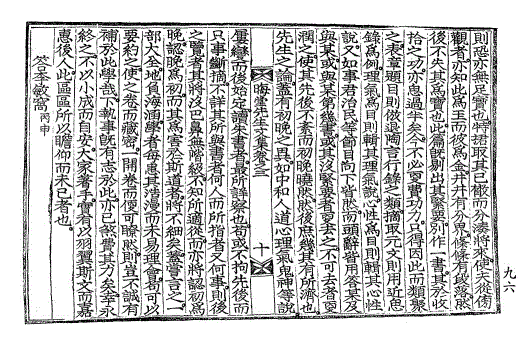 则恐亦无足宝也。特捃取其已散而分凑将来。使夫从傍观者。亦知此为玉而彼为金。井井有分界。条条有段落。然后不失其为宝也。此篇既剔出其紧要。别作一书。其于收拾之功。亦思过半矣。今不必更费功力。只得因此而类聚之。表章题目则仿退陶言行录之类。摘取元文则用近思录为例。理气为目则辑其理气说。心性为目则辑其心性说。又如事君治民等节目向下皆然。而头辞皆用答某及与某。或与某第几书。或其没紧要者更去之。不可去者更润之。使其先后不紊而初晚晓然。然后庶几其有所济也。先生之论。盖有初晚之异。如中和人道心理气鬼神等说。屡变而后始定。读朱书者。最所详察也。苟或不拘先后而只事断摘。不详其所与书者何人而所指者又何事。则后之览者其将没巴鼻无阶级。不知所适从。而亦将认初为晚。认晚为初。而其为害于斯道者。将不细矣。盖尝言之。一部大全。地负海涵。学者每患其浩漫而未易理会。苟可以要约之。使之卷而藏密。一开卷而便可瞭然。则岂不诚有补于此学哉。下执事既有志于此。亦已煞费其力矣。幸永终之。不以小成而自安。大家著手。实有以羽翼斯文而嘉惠后人。此区区所以瞻仰而未已者也。
则恐亦无足宝也。特捃取其已散而分凑将来。使夫从傍观者。亦知此为玉而彼为金。井井有分界。条条有段落。然后不失其为宝也。此篇既剔出其紧要。别作一书。其于收拾之功。亦思过半矣。今不必更费功力。只得因此而类聚之。表章题目则仿退陶言行录之类。摘取元文则用近思录为例。理气为目则辑其理气说。心性为目则辑其心性说。又如事君治民等节目向下皆然。而头辞皆用答某及与某。或与某第几书。或其没紧要者更去之。不可去者更润之。使其先后不紊而初晚晓然。然后庶几其有所济也。先生之论。盖有初晚之异。如中和人道心理气鬼神等说。屡变而后始定。读朱书者。最所详察也。苟或不拘先后而只事断摘。不详其所与书者何人而所指者又何事。则后之览者其将没巴鼻无阶级。不知所适从。而亦将认初为晚。认晚为初。而其为害于斯道者。将不细矣。盖尝言之。一部大全。地负海涵。学者每患其浩漫而未易理会。苟可以要约之。使之卷而藏密。一开卷而便可瞭然。则岂不诚有补于此学哉。下执事既有志于此。亦已煞费其力矣。幸永终之。不以小成而自安。大家著手。实有以羽翼斯文而嘉惠后人。此区区所以瞻仰而未已者也。答李敏窝(丙申)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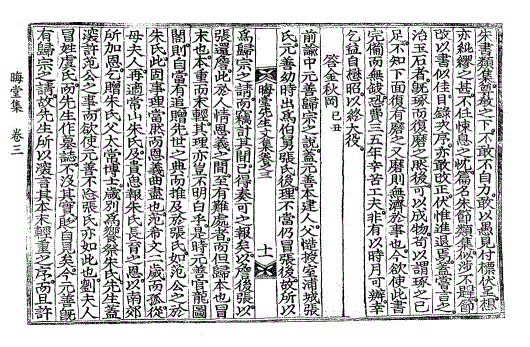 朱书类集。尊教之下。不敢不自力。敢以愚见付标伏呈。想亦纰缪之甚。不任悚息之忱。篇名朱节类集。似涉不韪。节改以书似佳。目录次序。亦敢改正。伏惟进退焉。盖尝言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然后。可以成物。苟以谓琢之已足。不知下面复有磨之又磨则无济于事也。今欲使此书完备而无缺。恐费三五年辛苦工夫。非有以时月可办。幸乞益自懋昭。以终大役。
朱书类集。尊教之下。不敢不自力。敢以愚见付标伏呈。想亦纰缪之甚。不任悚息之忱。篇名朱节类集。似涉不韪。节改以书似佳。目录次序。亦敢改正。伏惟进退焉。盖尝言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然后。可以成物。苟以谓琢之已足。不知下面复有磨之又磨则无济于事也。今欲使此书完备而无缺。恐费三五年辛苦工夫。非有以时月可办。幸乞益自懋昭。以终大役。答金秋冈(己丑)
前谕中元善归宗之说。盖元善本建人。父慥授室浦城张氏。元善幼时出为伯舅张氏后。理不当仍冒张后。故所以为归宗之请。而窃计其间。已得奏可之报矣。以詹后张。以张还詹。此于人情恩义之间。至有难处者。而但归本也冒末也。本重而末轻。其理亦岂不明白乎。是时元善官龙图阁。则自当有追赠先世之典而推及于张氏。如范公之于朱氏。此固事理当然而恩义曲尽也。范希文二岁而孤。从母夫人。再适常山朱氏。及贵思报朱氏长育之恩。以南郊所加恩。乞赠朱氏父太常博士。岁别为飨祭朱氏。先生盖深许范公之事。而欲使元善不忘张氏亦如此也。刘夫人冒姓虞氏。而先生作墓志。不没其实。贬自见矣。今元善既有归宗之请。故先生所以深言其本末轻重之序。而且许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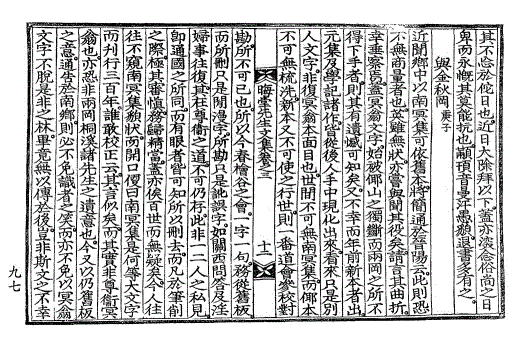 其不忘于佗日也。近日大除拜以下。盖亦深念俗尚之日卑而永慨其莫能抗也。颟顸音曼汗愚貌。退书多有之。
其不忘于佗日也。近日大除拜以下。盖亦深念俗尚之日卑而永慨其莫能抗也。颟顸音曼汗愚貌。退书多有之。与金秋冈(庚子)
近闻乡中以南冥集可依旧本。将简通于晋阳云。此则恐不无商量者也。英虽无状。亦尝与闻其役矣。请言其曲折。幸垂察焉。盖冥翁文字。始被倻山之独断而两冈之所不得下手者。则其有遗憾可知矣。又不幸而年前新本者出。元集及学记诸作。皆从后人手中现化出来。看来只是别人文字。非复冥翁本面目也。世间不可无南冥集。而倻本不可无梳洗。新本又不可使之行世。则一番道会参校对勘。所不可已也。所以今春桧谷之会。一字一句。务从旧板。而所删只是閒漫字。所勘只是讹误字。如关西问答及淫妇事往复。其在尊卫之道。不可仍存。此非一二人之私见。即通国之所同。而有眼者皆可知所以删去。而凡于笔削之际。极其审慎。务归精当。盖亦俟百世而无疑矣。今人往往不窥南冥集貌状。而开口便曰南冥集是何等大文字而刊行三百年。谁敢校正云。其言似矣。而其实非尊卫冥翁也。亦恐非两冈桐溪诸先生之遗意也。今又以仍旧板之意。通告于南乡。则必不免识者之笑。而亦不免以冥翁文字不脱是非之林。毕竟无以传于后。岂非斯文之不幸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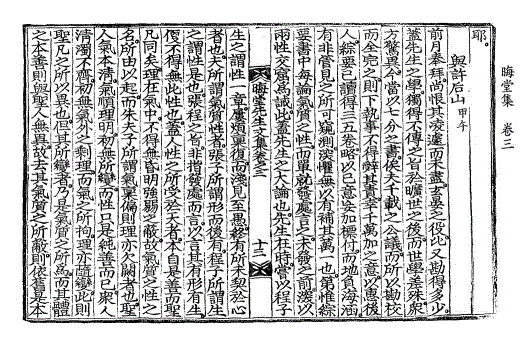 耶。
耶。与许后山(甲午)
前月奉拜。尚恨其凌遽而未尽。玄晏之役。比又勘得多少。盖先生之学。独得不传之旨于旷世之后。而世学差殊。众方惊异。今当以七分之书。俟夫千载之公议。而所以勘校而全完之。则下执事不得辞其责。幸千万加之意。以惠后人。综要已读得三五卷。略以己意妄加标付。而地负海涵。有非管见之所可窥测。深惧无以有补其万一也。第惟综要书中每论气质之性。而单就发处言之。未发之前。深以两性交窟为诫。此盖先生之大论也。先生在时。尝以程子生之谓性一章。屡烦禀复。而浅见至愚。终有所未契于心者也。夫所谓气质性者。张子所谓形而后有。程子所谓生之谓性是也。张程之旨。非指发处而言。以言其有形有生。便不得无此性也。盖人性之所受于天者。本自是善而圣凡同矣。理在气中。不得无昏明强弱之蔽。故气质之性之名。所由以起。而朱夫子所谓气禀偏则理亦欠阙者也。圣人气本清。气顺理明。初无所变。而性只是纯善而已。众人清浊不齐。初无气外之剩理。而气之所拘。理亦随变。此则圣凡之所以异也。但其所变者。乃是气质之所为。而其体之本善则与圣人无异。故去其气质之所蔽。则依旧是本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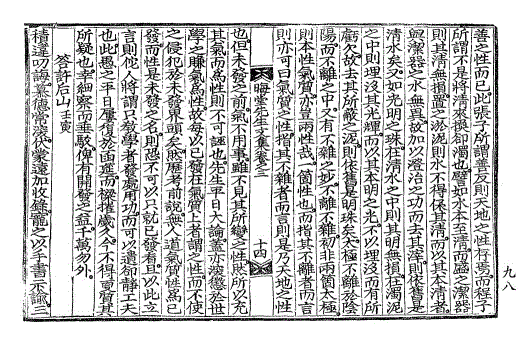 善之性而已。此张子所谓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而程子所谓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也。譬如水本至清。而盛之洁器则其清无损。置之淤泥则水不得保其清。而以其本清者。与洁器之水无异。故加以澄治之功而去其滓。则依旧是清水矣。又如光明之珠。在清水之中则其明无损。在浊泥之中则埋没其光辉。而以其本明之光。不以埋没而有所亏欠。故去其所蔽之泥。则依旧是明珠矣。太极不离于阴阳。而不离之中。又有不杂之妙。不离不杂。初非两个太极。则本性气质。亦岂两性哉。一个性也。而指其不离者而言则亦可曰气质之性。指其不杂者而言则是乃天地之性也。但未发之前。气不用事。虽不见其所变之性。然所以充其气而为性则不可诬也。先生平日大论。盖亦深惩于世学之赚气为性。故每以已发在气质上者谓之性。而不使之侵犯于未发界头矣。然历考前说。无人道气质性为已发。而性是未发之名。则恐不可以只就已发看。且以此立言则佗人将谓只教学者发处用功。而可以遗却静工夫也。此愚之平日屡复于函筵。而梁摧岁久。今不得更质其所疑也。幸细察而垂驳。俾有开发之益。千万勿外。
善之性而已。此张子所谓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焉。而程子所谓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也。譬如水本至清。而盛之洁器则其清无损。置之淤泥则水不得保其清。而以其本清者。与洁器之水无异。故加以澄治之功而去其滓。则依旧是清水矣。又如光明之珠。在清水之中则其明无损。在浊泥之中则埋没其光辉。而以其本明之光。不以埋没而有所亏欠。故去其所蔽之泥。则依旧是明珠矣。太极不离于阴阳。而不离之中。又有不杂之妙。不离不杂。初非两个太极。则本性气质。亦岂两性哉。一个性也。而指其不离者而言则亦可曰气质之性。指其不杂者而言则是乃天地之性也。但未发之前。气不用事。虽不见其所变之性。然所以充其气而为性则不可诬也。先生平日大论。盖亦深惩于世学之赚气为性。故每以已发在气质上者谓之性。而不使之侵犯于未发界头矣。然历考前说。无人道气质性为已发。而性是未发之名。则恐不可以只就已发看。且以此立言则佗人将谓只教学者发处用功。而可以遗却静工夫也。此愚之平日屡复于函筵。而梁摧岁久。今不得更质其所疑也。幸细察而垂驳。俾有开发之益。千万勿外。答许后山(壬寅)
积违叨诲。慕德常深。伏蒙远加收录。宠之以手书示谕。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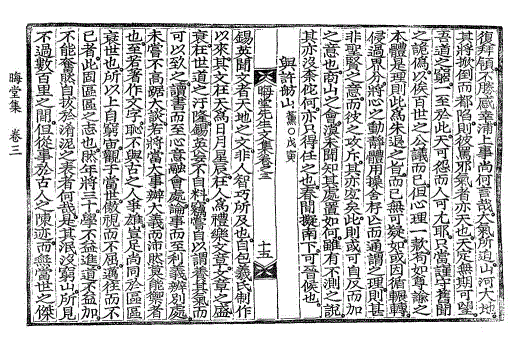 复拜领。不胜感幸。浦上事尚何言哉。大气所迫。山河大地。其将掀倒而都陷。则彼骂邪气者亦天也。天定无期可望。吾道之穷。一至于此。天可怨而人可尤耶。只当谨守旧闻之诡伪。以俟百世之公议而已。但心理一款。苟如尊谕之本体是理则此为朱退之旨。而已无可疑。如或因循辗转。侵过界分。将心之动静体用操舍存亡而通谓之理。则甚非圣贤之意。而彼之攻斥。其亦宜矣。此则或可自反而加之意也。商山之会。漠未闻知其处置如何。虽有不测之说。其亦没柰佗何。亦只得任之也。春间拟南下。可晋候也。
复拜领。不胜感幸。浦上事尚何言哉。大气所迫。山河大地。其将掀倒而都陷。则彼骂邪气者亦天也。天定无期可望。吾道之穷。一至于此。天可怨而人可尤耶。只当谨守旧闻之诡伪。以俟百世之公议而已。但心理一款。苟如尊谕之本体是理则此为朱退之旨。而已无可疑。如或因循辗转。侵过界分。将心之动静体用操舍存亡而通谓之理。则甚非圣贤之意。而彼之攻斥。其亦宜矣。此则或可自反而加之意也。商山之会。漠未闻知其处置如何。虽有不测之说。其亦没柰佗何。亦只得任之也。春间拟南下。可晋候也。与许舫山(薰○戊寅)
锡英闻文者天地之文。非人智巧所及也。自包羲氏制作以来。其文在天为日月星辰。在人为礼乐文章。文章之盛衰。在世道之污隆。锡英妄不自料。窃尝自以谓养其气而可以致之。读书而至心意融会处。论事而至利义辨别处。未尝不高踞大谈。若将当大事办大义而沛然莫能御者也。至若著作文字。耻不与古之人争雄。岂足尚同于区区衰世也。所以上自穷宙。观于当世。傲视而不屈。迈往而不已者。此固区区之志也。然年将三十。学不益进。道不益加。不能奋然自拔于淆泥之表者何哉。是其泯没穷山。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但从事于古人之陈迹。而无当世之杰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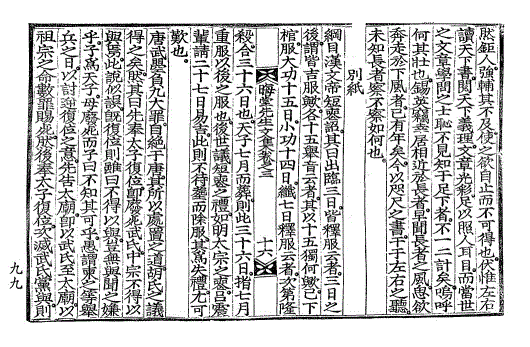 然钜人。强辅其不及。使之欲自止而不可得也。伏惟左右读天下书。阅天下义理。文章光彩。足以照人耳目。而当世之文章学问之士耻不见知于足下者。不一二计矣。呜呼何其壮也。锡英窃幸居相近于长者。早闻长者之风。思欲奔走于下风者。已有年矣。今以咫尺之书。干于左右之听。未知长者察不察如何也。
然钜人。强辅其不及。使之欲自止而不可得也。伏惟左右读天下书。阅天下义理。文章光彩。足以照人耳目。而当世之文章学问之士耻不见知于足下者。不一二计矣。呜呼何其壮也。锡英窃幸居相近于长者。早闻长者之风。思欲奔走于下风者。已有年矣。今以咫尺之书。干于左右之听。未知长者察不察如何也。别纸
纲目汉文帝短丧诏。其曰出临三日。皆释服云者。三日之后。谓皆吉服欤。各十五举音云者。其以十五独何欤。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云者。次第隆杀。合三十六日也。天子七月而葬。则此三十六日。指七月重服以后之服也。后世议短丧之礼。如明太宗之丧。吕震辈请二十七日易吉。此则不待葬而除服。其为失礼。尤可叹也。
唐武瞾负九大罪。自绝于唐。其所以处置之道。胡氏之议得之矣。然其曰先奉太子复位。即废死武氏。中宗不得以与焉。此说似误。既复位则虽曰不得以与。岂无与闻之嫌乎。子为天子。母废死而子曰不知其可乎。愚谓柬之等举兵之日。以讨逆复位之意。先告太庙。即以武氏至太庙。以祖宗之命数罪赐死。然后奉太子复位。次灭武氏党与。则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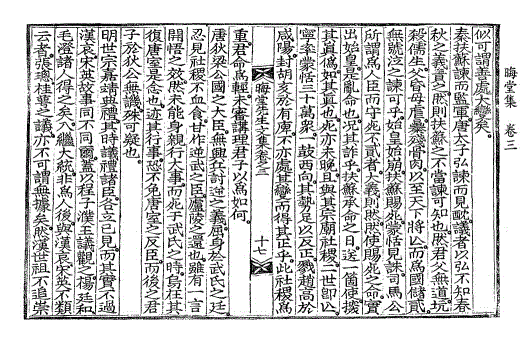 似可谓善处大变矣。
似可谓善处大变矣。秦扶苏谏而监军。唐太子弘谏而见酖。议者以弘不知春秋之义责之。然则扶苏之不当谏可知也。然君父无道。坑杀儒生。父昏母虐。㬥残骨肉。以至天下将亡。而为国储贰。无号泣之谏可乎。始皇始崩。扶苏赐死。蒙恬见诛。司马公所谓为人臣而守死不贰者。大义则然。然使赐死之命。实出始皇。是乱命也。况其诈乎。扶苏承命之日。送一个使。探其真伪。如其真也。死亦未晚。且与其宗庙社稷。二世即亡。宁率蒙恬三十万众。一鼓西向。其势足以反正。戮赵高于咸阳。封胡亥于有庳。不亦处其变而得其正乎。此社稷为重。君命为轻。未审讲理君子以为如何。
唐狄梁公国之大臣。无兴兵讨逆之义。屈身于武氏之廷。忍见社稷不血食。甘作逆武之臣。庐陵之还也。虽有一言开悟之效。然未能身亲行大事。而死于武氏之时。乌在其复唐室是念也。迹其行事。恐不免唐室之反臣。而后之君子于狄公无讥。殊可疑也。
明世宗嘉靖典礼。其时议礼诸臣。各立己见。而其实不过汉哀,宋英故事同不同尔。盖以程子濮王议观之。杨廷和,毛澄诸人得之矣。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云者。张璁,桂萼之议。亦不可谓无据矣。然汉世祖不追崇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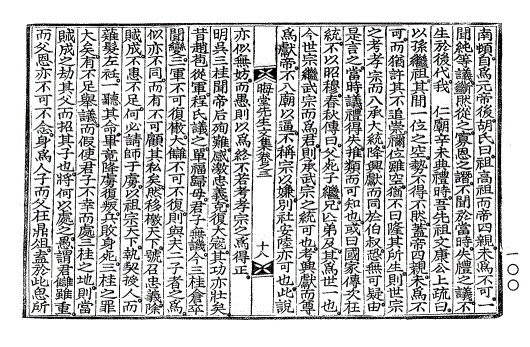 南顿。自为元帝后。胡氏曰。祖高祖而帝四亲。未为不可。一闻纯等议。断然从之。寡恩之谮。不闻于当时。失礼之议。不生于后代。我 仁庙辛未典礼时。吾先祖文康公上疏曰。以孙继祖。其间一位之空。势不得不然。盖帝四亲。未为不可。而犹许其不追崇。祢位虽空。犹不曰隆其所生。则世宗之考孝宗而入承大统。降兴献而同于伯叔。恐无可疑。由是言之。当时议礼得失。推类而可知也。或曰国家传次在统。不以昭穆。春秋传曰。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其为世一也。今世宗继武宗而为君。则承武宗之统可也。考兴献而尊为献帝。不入庙以逼。不称宗以嫌。别社安陆亦可也。此说亦似无妨。而愚则以为终不若考孝宗之为得正。
南顿。自为元帝后。胡氏曰。祖高祖而帝四亲。未为不可。一闻纯等议。断然从之。寡恩之谮。不闻于当时。失礼之议。不生于后代。我 仁庙辛未典礼时。吾先祖文康公上疏曰。以孙继祖。其间一位之空。势不得不然。盖帝四亲。未为不可。而犹许其不追崇。祢位虽空。犹不曰隆其所生。则世宗之考孝宗而入承大统。降兴献而同于伯叔。恐无可疑。由是言之。当时议礼得失。推类而可知也。或曰国家传次在统。不以昭穆。春秋传曰。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其为世一也。今世宗继武宗而为君。则承武宗之统可也。考兴献而尊为献帝。不入庙以逼。不称宗以嫌。别社安陆亦可也。此说亦似无妨。而愚则以为终不若考孝宗之为得正。明吴三桂闻帝后殉难。感激忠义。克复大寇。其功亦壮矣。昔赵苞从军。程氏议之。单福归母。君子无讥。今三桂仓卒闻变。三军不可复散。大雠不可不复。则与夫二子者之为。似亦不同。而有不可顾其私矣。然移檄天下。号召忠义。除贼成。不患不足。何必请师于虏。以祖宗天下。执契授人。而薙发左衽。一听其命。毕竟降虏复叛。兵败身死。三桂之罪大矣。有不足举议。而假使君子不幸而处三桂之地。则当贼成之劫其父而招其子也。将何以处之。愚谓君雠虽重。而父恩亦不可不念。身为人子而父在鼎俎。盍于此思所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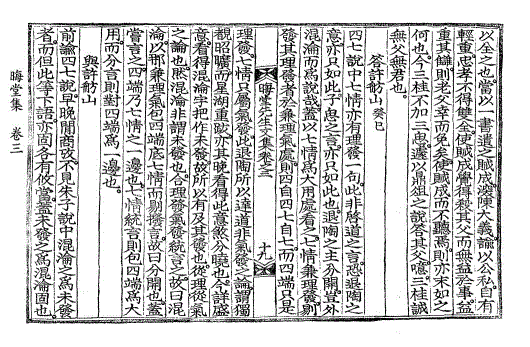 以全之也。当以一书遗之贼成。深陈大义。谕以公私。自有轻重。忠孝不得双全。使贼成觉得杀其父而无益于事。益重其雠。则老父幸而免矣。使贼成而不听焉。则亦末如之何也。今三桂不加三思。遽以鼎俎之说答其父。噫。三桂诚无父无君也。
以全之也。当以一书遗之贼成。深陈大义。谕以公私。自有轻重。忠孝不得双全。使贼成觉得杀其父而无益于事。益重其雠。则老父幸而免矣。使贼成而不听焉。则亦末如之何也。今三桂不加三思。遽以鼎俎之说答其父。噫。三桂诚无父无君也。答许舫山(癸巳)
四七说中七情亦有理发一句。此非启道之言。恐退陶之意。亦只如此。子思之言。亦只如此也。退陶之主分开。岂外混沦而为说哉。盖以七情为大用处看之。七情兼理发。剔发其理发者于兼理气处。则四自四七自七。而四端只是理发。七情只属气发。此退陶所以达道非气发之论。谓独睹昭旷。而星湖重跋。亦其晚看得此意煞分晓也。今详盛意。看得混沦字把作未发。故所以有及其发也。从理从气之论也。然混沦非谓未发也。合理发气发统言之。故曰混沦。以那兼理气包四端底七情而剔拨言。故曰分开也。盖尝言之。四端乃七情之一边也。七情统言则包四端为大用。而分言则对四端为一边也。
与许舫山
前谕四七说。早晚閒商考。不见朱子说中混沦之为未发者。而但此等下语。亦固各有攸当。盖未发之为混沦固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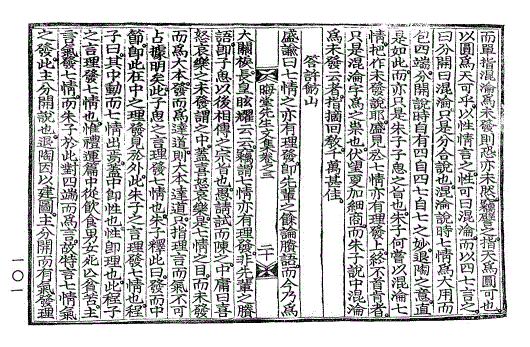 而单指混沦为未发则恐亦未然。窃譬之。指天为圆可也。以圆为天可乎。以性情言之。性可曰混沦。而以四七言之。曰分开曰混沦。只是分合说也。混沦说时七情为大用而包四端。分开说时自有四自四七自七之妙。退陶之意。直是如此。而亦只是朱子子思之旨也。朱子何尝以混沦七情。把作未发说耶。盛见于七情亦有理发上。终不首肯者。只是混沦字为之祟也。伏望更加细商。而朱子说中混沦为未发云者。指摘回教。千万甚佳。
而单指混沦为未发则恐亦未然。窃譬之。指天为圆可也。以圆为天可乎。以性情言之。性可曰混沦。而以四七言之。曰分开曰混沦。只是分合说也。混沦说时七情为大用而包四端。分开说时自有四自四七自七之妙。退陶之意。直是如此。而亦只是朱子子思之旨也。朱子何尝以混沦七情。把作未发说耶。盛见于七情亦有理发上。终不首肯者。只是混沦字为之祟也。伏望更加细商。而朱子说中混沦为未发云者。指摘回教。千万甚佳。答许舫山
盛谕曰七情之亦有理发。即先辈之馀论剩语。而今乃为大关棙。长皇眩耀云云。窃谓七情亦有理发。非先辈之剩语。即子思以后相传之宗旨也。愚请试而陈之。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盖喜怒哀乐。是七情之目。而未发而为大本。发而为达道。则大本达道。只指理言而气不可占据明矣。此子思之言理发七情也。朱子释此曰。发而中节。即此在中之理发见于外。此朱子之言理发七情也。程子曰。其中动而七情出焉。盖中即性也。性即理也。此程子之言理发七情也。惟礼运篇中从饮食男女死亡贫苦。主言气发七情。而朱子于此对四端而为言。故特言七情气之发。此主分开说也。退陶因以建图。主分开而有气发理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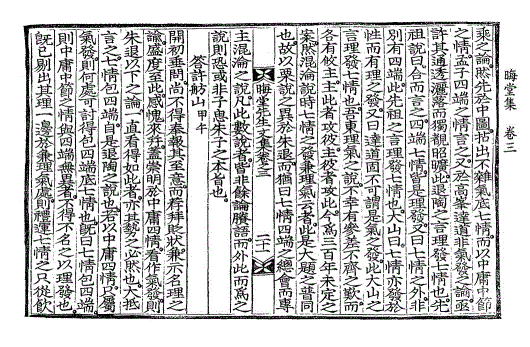 乘之论。然先于中图。拈出不杂气底七情。而以中庸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言之。又于高峰达道非气发之论。亟许其通透洒落而独睹昭旷。此退陶之言理发七情也。先祖说曰。合而言之。四端七情。皆是理发。又曰七情之外。非别有四端。此先祖之言理发七情也。大山曰。七情亦发于性而有理之发。又曰达道固不可谓是气之发。此大山之言理发七情也。吾东理气之说。不幸有参差不齐之叹。而各有攸主。主此者攻彼。主彼者攻此。今为三百年未定之案。然混沦说时七情之发兼理气云者。此是大题之普同也。故以栗说之异于朱退。而犹曰七情四端之总会而专主混沦之说。凡此数说者。皆非馀论剩语。而外此而为之说则恐或非子思朱子之本旨也。
乘之论。然先于中图。拈出不杂气底七情。而以中庸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言之。又于高峰达道非气发之论。亟许其通透洒落而独睹昭旷。此退陶之言理发七情也。先祖说曰。合而言之。四端七情。皆是理发。又曰七情之外。非别有四端。此先祖之言理发七情也。大山曰。七情亦发于性而有理之发。又曰达道固不可谓是气之发。此大山之言理发七情也。吾东理气之说。不幸有参差不齐之叹。而各有攸主。主此者攻彼。主彼者攻此。今为三百年未定之案。然混沦说时七情之发兼理气云者。此是大题之普同也。故以栗说之异于朱退。而犹曰七情四端之总会而专主混沦之说。凡此数说者。皆非馀论剩语。而外此而为之说则恐或非子思朱子之本旨也。答许舫山(甲午)
开初垂问。尚不得奉报其至意。而荐拜贬状。兼示名理之谕。盛度至此。感愧来并。盖崇明于中庸四情。看作气发。则朱退以下之论。一直看得如此者。亦其势之必然也。大抵言之。七情包四端。自是退陶之说也。若以中庸四情。只属气发。则何处可讨得包四端底七情也。既曰七情包四端。则中庸中节之情与四端无异者。不得不名之以理发也。既已剔出其理一边于兼理气处。则礼运七情之只从饮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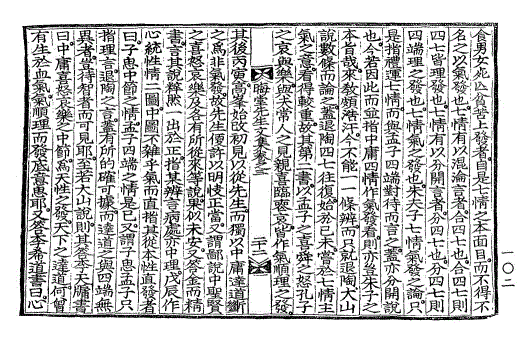 食男女死亡贫苦上发者。自是七情之本面目。而不得不名之以气发也。七情有以混沦言者。合四七也。合四七则四七皆理发也。七情有以分开言者。分四七也。分四七则四端理之发也。七情气之发也。朱夫子七情气发之论。只是指礼运七情。而与孟子四端对待而言之。盖亦分开说也。今若因此而并指中庸四情作气发看。则亦岂朱子之本旨哉。来教颇浩汗。今不能一一条辨。而只就退陶,大山说数条而论之。盖退陶四七往复。始于己未。尝于七情主气之意。看得较重。故其第二书。以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与夫常人之见亲喜临丧哀。皆作气顺理之发。其后丙寅。高峰始改初见以从先生。而独以中庸达道断之为非气发。故先生便许以明快正当。又谓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未安。又答金而精书。言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指某辨言病处亦中理。戊辰作心统性情二图。中图不杂乎气而直指其从本性直发者曰。子思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是已。又谓子思孟子只指理言。退陶之言。盖有所的确可据。而达道之与四端无异者。岂待智者而可见耶。至若大山说。则其答李天牖书曰。中庸喜怒哀乐之中节。为天性之发。天下之达道。何曾有生于血气。气顺理而发底意思耶。又答李希道书曰。心
食男女死亡贫苦上发者。自是七情之本面目。而不得不名之以气发也。七情有以混沦言者。合四七也。合四七则四七皆理发也。七情有以分开言者。分四七也。分四七则四端理之发也。七情气之发也。朱夫子七情气发之论。只是指礼运七情。而与孟子四端对待而言之。盖亦分开说也。今若因此而并指中庸四情作气发看。则亦岂朱子之本旨哉。来教颇浩汗。今不能一一条辨。而只就退陶,大山说数条而论之。盖退陶四七往复。始于己未。尝于七情主气之意。看得较重。故其第二书。以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与夫常人之见亲喜临丧哀。皆作气顺理之发。其后丙寅。高峰始改初见以从先生。而独以中庸达道断之为非气发。故先生便许以明快正当。又谓鄙说中圣贤之喜怒哀乐及各有所从来等说。果似未安。又答金而精书。言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指某辨言病处亦中理。戊辰作心统性情二图。中图不杂乎气而直指其从本性直发者曰。子思中节之情。孟子四端之情是已。又谓子思孟子只指理言。退陶之言。盖有所的确可据。而达道之与四端无异者。岂待智者而可见耶。至若大山说。则其答李天牖书曰。中庸喜怒哀乐之中节。为天性之发。天下之达道。何曾有生于血气。气顺理而发底意思耶。又答李希道书曰。心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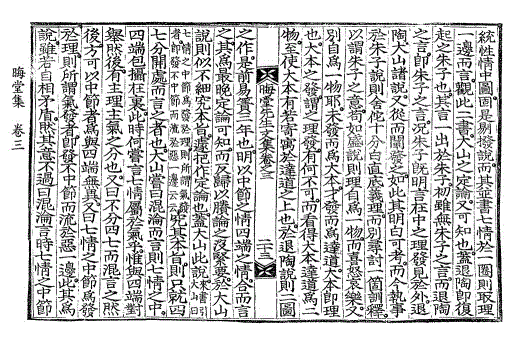 统性情中图。固是剔拨说。而其并书七情于一圈则取理一边而言。观此二书。大山之定论。又可知也。盖退陶即复起之朱子也。其言一出于朱子。初虽无朱子之言。而退陶之言。即朱子之言。况朱子既明言在中之理发见于外。退陶,大山诸说。又从而阐发之。如此其明白可考。而今执事于朱子说则舍佗十分白直底义理。而别寻讨一个训释。以谓朱子之意。苟如盛说则理自为一物。而喜怒哀乐。又别自为一物耶。未发而为大本。才发而为达道。大本即理也。大本之发。谓之理发。有何不可。而看得大本达道为二物。至使大本有若寄寓于达道之上也。于退陶说则二图之作。是前易箦三年也。明以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合而言之。其为最晚定论可知。而反归以剩论之没紧要。于大山说则似不细究本旨。遽把作定论也。盖大山此说。(来书引大山曰七情之中节为发于理。则所谓气发者。即发不中节而流于恶一边云云。)究其本旨。则只就四七分开处而言之者也。大山尝曰混沦而言则七情之中。四端包摄在里。此时何尝言七情属于气乎。惟与四端对举然后。有主理主气之分也。又曰不分四七而混言之然后。方可以中节者为与四端无异。又曰七情之中节为发于理。则所谓气发者。即发不中节而流于恶一边。此其为说。虽若自相矛盾。然其意不过曰混沦言时七情之中节
统性情中图。固是剔拨说。而其并书七情于一圈则取理一边而言。观此二书。大山之定论。又可知也。盖退陶即复起之朱子也。其言一出于朱子。初虽无朱子之言。而退陶之言。即朱子之言。况朱子既明言在中之理发见于外。退陶,大山诸说。又从而阐发之。如此其明白可考。而今执事于朱子说则舍佗十分白直底义理。而别寻讨一个训释。以谓朱子之意。苟如盛说则理自为一物。而喜怒哀乐。又别自为一物耶。未发而为大本。才发而为达道。大本即理也。大本之发。谓之理发。有何不可。而看得大本达道为二物。至使大本有若寄寓于达道之上也。于退陶说则二图之作。是前易箦三年也。明以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合而言之。其为最晚定论可知。而反归以剩论之没紧要。于大山说则似不细究本旨。遽把作定论也。盖大山此说。(来书引大山曰七情之中节为发于理。则所谓气发者。即发不中节而流于恶一边云云。)究其本旨。则只就四七分开处而言之者也。大山尝曰混沦而言则七情之中。四端包摄在里。此时何尝言七情属于气乎。惟与四端对举然后。有主理主气之分也。又曰不分四七而混言之然后。方可以中节者为与四端无异。又曰七情之中节为发于理。则所谓气发者。即发不中节而流于恶一边。此其为说。虽若自相矛盾。然其意不过曰混沦言时七情之中节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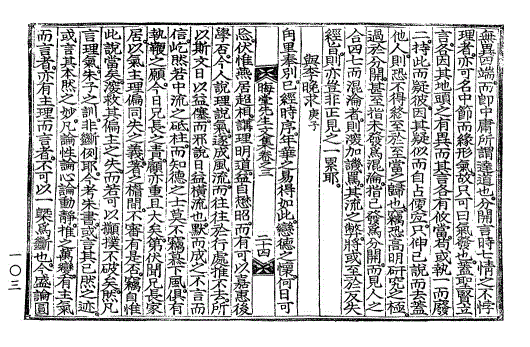 无异四端。而即中庸所谓达道也。分开言时七情之不悖理者。亦可名中节而缘形气。故只可曰气发也。盖圣贤立言。各因其地头之有异而其言各有攸当。苟或执一而废二。持此而疑彼。因其疑似而自占便宜。只伸己说而去盖他人。则恐不得终至于至当之归也。窃恐高明研究之极。过于分开。甚至指未发为混沦。指已发为分开。而见人之合四七而混沦者。则深加讥骂。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反失经旨。则亦岂非正见之一累耶。
无异四端。而即中庸所谓达道也。分开言时七情之不悖理者。亦可名中节而缘形气。故只可曰气发也。盖圣贤立言。各因其地头之有异而其言各有攸当。苟或执一而废二。持此而疑彼。因其疑似而自占便宜。只伸己说而去盖他人。则恐不得终至于至当之归也。窃恐高明研究之极。过于分开。甚至指未发为混沦。指已发为分开。而见人之合四七而混沦者。则深加讥骂。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反失经旨。则亦岂非正见之一累耶。与李晚求(庚子)
甪里奉别。已经时序。年华之易得如此。恋德之怀。何日可忘。伏惟燕居超相。讲理明道。益自懋昭。而有可以嘉惠后学否。今人说理说气。遂成风流。而往往于行处推不去。所以斯文日以益僿。而邪说日益横流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屹然若中流之砥柱。而知德之士莫不窃慕下风。俱有执鞭之愿。今日兄长之责。顾亦重且大矣。第伏闻兄长家居。以气主理偏同失之义。著之楣间。不审有是否。窃自惟此说当矣。深救其偏主之失。而若可以攧扑不破矣。然凡言理气。朱子之训。非断例耶。今考朱书。或言其已然之迹。或言其本然之妙。凡论性论心论动静。推之万变。有主气而言者。亦有主理而言者。不可以一槩为断也。今盛论圆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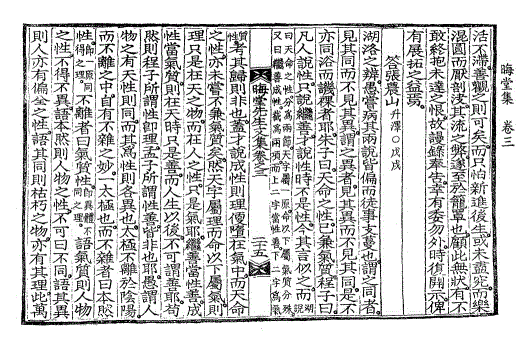 活不滞。善观之则可矣。而只怕新进后生。或未尽究。而乐混圆而厌剖决。其流之弊。遂至于笼罩也。顾此无状。有不敢终抱未达之恨。故谩录奉告。幸有委勿外。时复开示。俾有展拓之益焉。
活不滞。善观之则可矣。而只怕新进后生。或未尽究。而乐混圆而厌剖决。其流之弊。遂至于笼罩也。顾此无状。有不敢终抱未达之恨。故谩录奉告。幸有委勿外。时复开示。俾有展拓之益焉。答张农山(升泽○戊戌)
湖洛之辨。愚尝病其两说皆偏而徒事支蔓也。谓之同者。见其同而不见其异。谓之异者。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是不亦同浴而讥裸者耶。朱子曰。天命之性。已兼气质。程子曰。凡人说性。只说继善。才说性时不是性。今其言似之。而(湖说曰天命之性。分为两节。天字属一原。命以下属气质分殊。又曰继善成性。截为两项。而上二字当性善。下二字为气质性。)考其归则非也。盖才说成性则理便堕在气中。而天命之性。亦未尝不兼气质矣。然天字属理而命以下属气。则理只是在天之物。而在人之性。只是气耶。继善当性善。成性当气质。则在天时只是善。而人生以后。不可谓善耶。苟然则程子所谓性即理。孟子所谓性善。皆非也耶。愚谓人物之有天性则同。而其为性则各异也。太极不离于阴阳。而不离之中。自有不杂之妙。一太极也。而不杂者曰本然性。(即一原同得之理。)不离者曰气质性。(即异体不同之理。)语气质则人物之性。不得不异。语本然则人物之性。不可曰不同。语其异则人亦有偏全之性。语其同则枯朽之物。亦有其理。此万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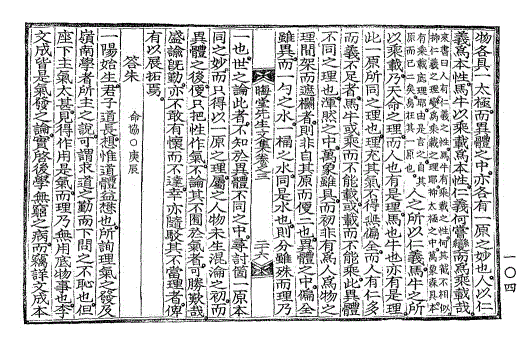 物各具一太极。而异体之中。亦各有一原之妙也。人以仁义为本性。马牛以乘载为本性。仁义何尝变而为乘载哉。(来书曰人有仁义之性。马牛有乘载之性。何其截不相似。抑仁义之理。变为乘载之理耶。抑太极之中。万象森具。本有乘载底理耶。由是言之。自其原而已二矣。乌在其一原也。)人之所以仁义。马牛之所以乘载。乃天命之理。而人也有是理。马也牛也亦有是理。此一原所同之理也。理充其气不得无偏全。而人有仁多而义不足者。马牛或乘而不能载。或载而不能乘。此异体不同之理也。浑然之中。万象虽具。而初非有为人为物之理间架而遮栏者。则非自其原而便二也。异体之中。偏全虽异。而一勺之水。一桶之水。同是水也。则分虽殊而理乃一也。世之论此者。不知于异体不同之中。寻讨个一原本同之妙。而只得以一原之理。属之人物未生混沦之初。而异体之后。便只把性作气。不论其不囿于气者。可胜叹哉。盛谕既勤。亦不敢有怀而不达。幸亦随驳其不当理者。俾有以展拓焉。
物各具一太极。而异体之中。亦各有一原之妙也。人以仁义为本性。马牛以乘载为本性。仁义何尝变而为乘载哉。(来书曰人有仁义之性。马牛有乘载之性。何其截不相似。抑仁义之理。变为乘载之理耶。抑太极之中。万象森具。本有乘载底理耶。由是言之。自其原而已二矣。乌在其一原也。)人之所以仁义。马牛之所以乘载。乃天命之理。而人也有是理。马也牛也亦有是理。此一原所同之理也。理充其气不得无偏全。而人有仁多而义不足者。马牛或乘而不能载。或载而不能乘。此异体不同之理也。浑然之中。万象虽具。而初非有为人为物之理间架而遮栏者。则非自其原而便二也。异体之中。偏全虽异。而一勺之水。一桶之水。同是水也。则分虽殊而理乃一也。世之论此者。不知于异体不同之中。寻讨个一原本同之妙。而只得以一原之理。属之人物未生混沦之初。而异体之后。便只把性作气。不论其不囿于气者。可胜叹哉。盛谕既勤。亦不敢有怀而不达。幸亦随驳其不当理者。俾有以展拓焉。答朱▣▣(命协○庚辰)
一阳始生。君子道长。想惟道体益懋也。所询理气之发及岭南学者所主之说。可谓求道之勤而下问之不耻也。但座下主气太甚。见得作用是气。而理乃无用底物事也。李文成皆是气发之论。实启后学无穷之病。而窃详文成本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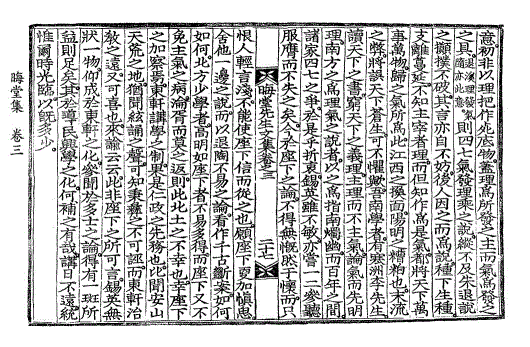 意。初非以理把作死底物。盖理为所发之主而气为发之之具。(退溪理发气随亦此意。)则四七气发理乘之说。纵不及朱退说之攧扑不破。其言亦自不妨。后人因之而为说。种下生种。支离蔓延。不知主宰者理。而但知作为是气。都将天下万事万物。归之气所为。此江西之换面。阳明之糟粕也。末流之弊。将误天下苍生。可不惧欤。吾南学者。有寒洲李先生。读天下之书。穷天下之义理。主理而不主气。论气而先明理。南方之为理气之说者。以之为指南烛幽。而百年之间。诸家四七之争。于是乎折衷。锡英虽不敏。亦尝一二参听服膺而不失之矣。今于座下之论。不得无慨然于怀。而只恨人轻言浅。不能使座下信而从之也。愿座下更加慎思。舍他一边之说。而以退陶不易之论。看作千古断案。如何如何。北方少学者。高明如座下者不易多得。而座下又不免主气之病。沦胥而莫之返。则此北土之不幸也。幸座下之加察焉。东轩讲学之制。果是仁政之先务也。比闻安山天荒之地。犹闻弦诵之声。可知秉彝之不可诬。而东轩治教之远。又可喜也。来谕云云。此非座下之所可言。锡英无状一物。仰成于东轩之化。参闻于多士之论。得有一斑所益则足矣。其于导民兴学之化。何补之有哉。讲日不远。统惟尔时光临。以既多少。
意。初非以理把作死底物。盖理为所发之主而气为发之之具。(退溪理发气随亦此意。)则四七气发理乘之说。纵不及朱退说之攧扑不破。其言亦自不妨。后人因之而为说。种下生种。支离蔓延。不知主宰者理。而但知作为是气。都将天下万事万物。归之气所为。此江西之换面。阳明之糟粕也。末流之弊。将误天下苍生。可不惧欤。吾南学者。有寒洲李先生。读天下之书。穷天下之义理。主理而不主气。论气而先明理。南方之为理气之说者。以之为指南烛幽。而百年之间。诸家四七之争。于是乎折衷。锡英虽不敏。亦尝一二参听服膺而不失之矣。今于座下之论。不得无慨然于怀。而只恨人轻言浅。不能使座下信而从之也。愿座下更加慎思。舍他一边之说。而以退陶不易之论。看作千古断案。如何如何。北方少学者。高明如座下者不易多得。而座下又不免主气之病。沦胥而莫之返。则此北土之不幸也。幸座下之加察焉。东轩讲学之制。果是仁政之先务也。比闻安山天荒之地。犹闻弦诵之声。可知秉彝之不可诬。而东轩治教之远。又可喜也。来谕云云。此非座下之所可言。锡英无状一物。仰成于东轩之化。参闻于多士之论。得有一斑所益则足矣。其于导民兴学之化。何补之有哉。讲日不远。统惟尔时光临。以既多少。答金泰瞻(戊戌)
儿还承谕为幸。孙妇延礼在即。六旬人世。滋况顾何如。既以贵第延妇则名目定矣。既定名目则其父过房。亦当以其前。定日行礼矣。然当日既有杯酌之设。宗族宾客之会。则聘子与延妇同日行之。而先行聘礼。次行见舅之礼。亦似简便。告庙则曰鲁东年今六十。未得胤子。窃惧承守无托。玆择从兄子熙台立以为嗣。熙台之子仁埴已娶于某郡某官姓名之女。以今某日延妇。当日兼行聘礼云云。未知如何。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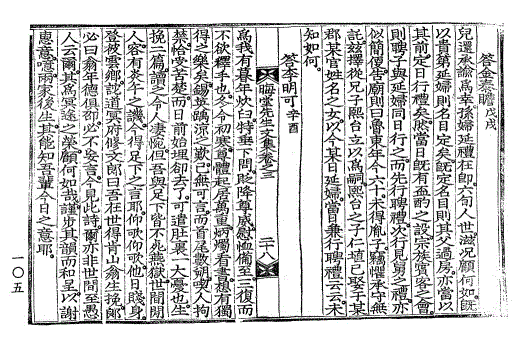 答李明可(辛酉)
答李明可(辛酉)为我有暮年炊臼。特垂下问。贬降尊威。慰恤备至。三复而不欲释手也。冬令初寒。尊体起居万重。炳烛看书。想有独得之乐矣。锡英踽凉之叹。已无可言。而首尾数朔。吃人拘禁。恰受苦楚。而日前始埋却去了。可遣肚里一大忧也。生挽二篇。读之令人凄惋。但吾与足下皆不死燕狱。世间閒人。容有炎午之讥。今得足下之言耶。仰㰤仰㰤。他日贱身。登彼云乡。詑道冥府修文郎曰吾在世得肯山翁生挽。郎必曰翁年德俱卲。必不妄言。今见此诗。尔亦非世间至愚人云尔。其为冥途之荣。顾何如哉。谨步其韵而和呈。以谢惠意。噫。两家后生。其能知吾辈今日之意耶。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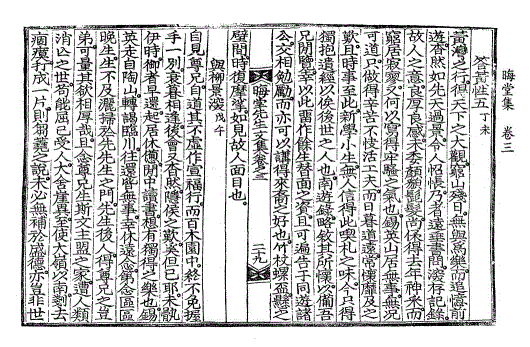 答黄性五(丁未)
答黄性五(丁未)黄湾之行。得天下之大观。穷山残日。无与为乐。而追忆前游。杳然如先天过景。令人怊怅。乃者远垂书问。深存记录。故人之意。良厚良感。未委颜貌髭发。尚保得去年神采。而穷居寂寥。又何以写得牢骚之气也。锡英山居无事。无况可道。只做得辛苦不快活工夫。而日暮道远。常怀靡及之叹。且时事至此。新学小生。无人信得此吃札之味。今只得独抱遗经以俟后世之人也。南游录。略叙其所怀。以备吾兄閒览。幸以此留作馀生替面之资。且可遍告于同游诸公。交相勉励。而亦可以讲得来裔之好也。竹杖螺杯。悬之壁间。时复摩挲。如见故人面目也。
与柳景深(戊午)
自见尊兄。自道其不虚作宣福行。而百木园中。终不免握手一别。衰暮相逢。后会又杳然。隐侯之叹。奚但已耶。未骫伊时。御者早还。起居休惫。閒中读书。想有独得之乐也。锡英走自陶山。转谒临川。往还皆无事。幸休远念。第念区区晚生。生不及洒扫于先先生之门。先生后人。得尊兄之岂弟。可量其欲相厚哉。且念尊兄生斯文主盟之家。遭人类消亡之世。苟能屈己受人。大舍崖异。至使大岭以南。刬去痼瘼。打成一片。则刍荛之说。未必无补于盛德。亦岂非世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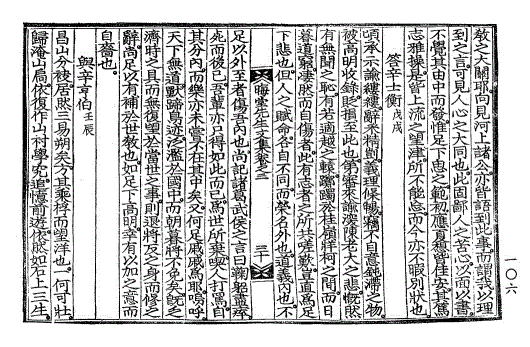 教之大关耶。向见河上诸公。亦皆语到此事。而谓我以理到之言。可见人心之大同也。此固鄙人之苦心。以面以书。不觉其由中而发。惟足下思之。范初,应夏想皆佳安。其笃志雅操。是皆上流之望津。所不能忘。而今亦不暇别状也。
教之大关耶。向见河上诸公。亦皆语到此事。而谓我以理到之言。可见人心之大同也。此固鄙人之苦心。以面以书。不觉其由中而发。惟足下思之。范初,应夏想皆佳安。其笃志雅操。是皆上流之望津。所不能忘。而今亦不暇别状也。答辛士衡(戊戌)
顷承示谕缕缕。辞采精剀。义理条畅。窃不自意钝滞之物。被高明收录。贬损至此也。第审来谕深陈老大之悲。慨然有无闻之耻。有若适越之辕。踯躅于桂岭牂柯之间。而日暮道穷。凄然而自伤者。此有志者之所共嗟叹。岂直为足下悲也。但人之赋命。各自不同。而荣名外也。道义内也。不足以外至者伤吾内也。尚记诸葛武侯之言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吾辈亦只得如此而已。为世所弃。吃人打骂。自其分内。而乐亦未尝不在其中矣。又何足戚戚为耶。呜呼。天下无道。兽蹄鸟迹。泛滥于国中。而朝暮将不免矣。既乏济时之具而无复望于当世之事。则退将反之身而修之辞。尚足以有补于世教也。如足下高明。幸有以加之意而自啬也。
与辛亨伯(壬辰)
昌山分袂。居然三易朔矣。方其乘桴而望洋也。一何可壮。归淹山扃。依复作山村学究。追忆前游。依然如石上三生。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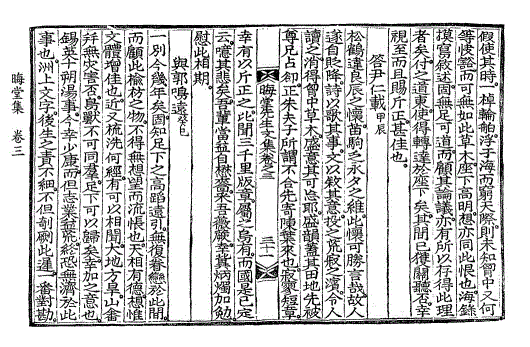 假使其时。一棹轮舶。浮于海而穷天际。则未知胸中又何等快豁。而可无如此草木。座下高明。想亦同此恨也。海录摸写叙述。固无足可道。而顾其论议。亦有所以存得此理者矣。付之道东。使得转达于座下矣。其间已获关听否。幸视至而且赐斤正。甚佳也。
假使其时。一棹轮舶。浮于海而穷天际。则未知胸中又何等快豁。而可无如此草木。座下高明。想亦同此恨也。海录摸写叙述。固无足可道。而顾其论议。亦有所以存得此理者矣。付之道东。使得转达于座下矣。其间已获关听否。幸视至而且赐斤正。甚佳也。答尹仁载(甲辰)
松鹤违良辰之怀。苗驹乏永夕之维。此怀可胜言哉。故人遂自贬降。诗以歌其事。文以叙其意。投之荒寂之滨。令人读之。消得胸中草木。盛意其可忘耶。盛韵盖其田地先被尊兄占却。正朱夫子所谓不合先寄陈叶来也。寂寥短章。幸有以斤正之。比闻三千里版章。属之乌有。而国是已定云。噫其悲矣。吾辈当益自懋啬。采吾薇蕨。幸冀炳烛加勉。慰此相期。
与郭鸣远(癸巳)
一别今几年矣。固知足下之高蹈远引。无复眷恋于此间。而顾此榆枋之物。不得无想望而流怅也。天相有德。想惟文体增佳也。近又梳洗何经。有可以相闻。大地方旱。山畬并无灾害否。鸟兽不可同群。足下可以归矣。幸加之意也。锡英十朔汤事。今幸少康。而但志业益荒。终恐无济于此事也。洲上文字。后生之责不细。不但剞劂此迟。一番对勘。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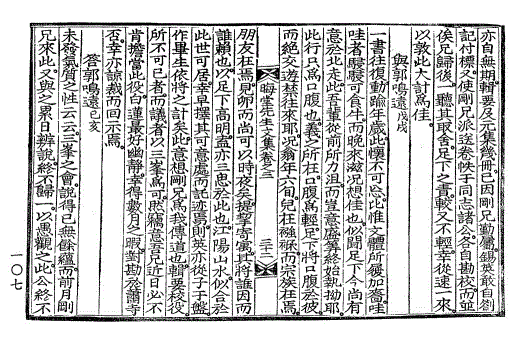 亦自无期。辑要及元集几册。已因刚兄勤属。锡英敢自劄记付标。又使刚兄派送卷帙于同志诸公。各自勘校。而并俟兄归后。一听其取舍。足下之责。较又不轻。幸从速一来。以敦此大计为佳。
亦自无期。辑要及元集几册。已因刚兄勤属。锡英敢自劄记付标。又使刚兄派送卷帙于同志诸公。各自勘校。而并俟兄归后。一听其取舍。足下之责。较又不轻。幸从速一来。以敦此大计为佳。与郭鸣远(戊戌)
一书往复。动踰年岁。此怀不可忘。比惟文体所履加啬。哇哇者骎骎可食牛。而晚来滋况想佳也。似闻足下今尚有意于北走。此吾辈从前所力沮。而岂意盛算终始执拗耶。此行只为口腹也。义之所在。口腹为轻。足下将口腹于彼。而绝交游禁往来耶。况翁年六旬。儿在襁褓。而宗族在焉。朋友在焉。见卵而尚可以时夜矣。提挈寄寓。其将谁因而谁赖也。以足下高明。盍亦三思于此也。江阳山水。似合于此世可居。幸早择其可意处而托迹焉。则英亦从子于盘。作毕生依将之计矣。此意想刚兄为我传道也。辑要校役。所不可已者。而议者以三峰为可。然窃意吾兄近日必不肯担当此役。白莲最好幽静。幸得数月之暇。对勘于萧寺否。幸亦谅裁而回示焉。
答郭鸣远(己亥)
未发气质之性云云。三峰之会。说得已无馀蕴。而前月刚兄来此。又与之累日辨说。终不归一。以愚观之。此公终不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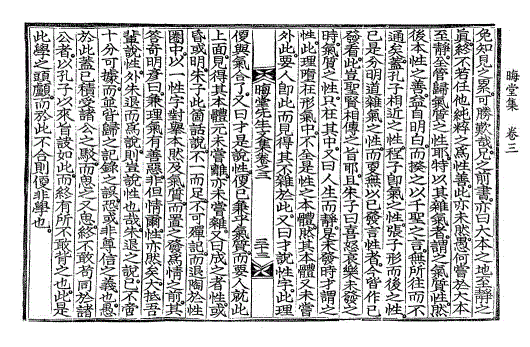 免知见之累。可胜叹哉。兄之前书。亦曰大本之地至静之真。终不若任他纯粹之为性善。此亦未然。愚何尝于大本至静。全管归气质之性耶。特以其杂气者。谓之气质性。然后本性之善。益自明白。而揆之以千圣之言。无所往而不通矣。盖孔子相近之性。程子即气之性。张子形而后之性。已是分明道杂气之性。而更无以已发言性者。今皆作已发看。此岂圣贤相传之旨耶。且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质之性。只在其中。又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才谓之性。此理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然其本体又未尝外此。要人即此而见得其不杂于此。又曰才说性字。此理便与气合了。又曰才是说性。便已兼乎气质。而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又曰成之者性。或昏或明。朱子此个话说。不一而足。不可殚记。而退陶于性圈中。以一性字对举本然及气质。而置之发为情之前。其答奇明彦曰。兼理气有善恶。非但情尔。性亦然矣。大抵吾辈说性。外朱退而为说。则岂说性也哉。朱退之说。已不啻十分可据。而并皆归之记录之误。恐或非尊信之义也。愚于此盖已积受诸公之驳。而思之又思。终不敢苟同于诸公者。以孔子以来旨诀如此。而终有所不敢背之也。此是此学之头颅。而于此不合则便非学也。
免知见之累。可胜叹哉。兄之前书。亦曰大本之地至静之真。终不若任他纯粹之为性善。此亦未然。愚何尝于大本至静。全管归气质之性耶。特以其杂气者。谓之气质性。然后本性之善。益自明白。而揆之以千圣之言。无所往而不通矣。盖孔子相近之性。程子即气之性。张子形而后之性。已是分明道杂气之性。而更无以已发言性者。今皆作已发看。此岂圣贤相传之旨耶。且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质之性。只在其中。又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才谓之性。此理堕在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然其本体又未尝外此。要人即此而见得其不杂于此。又曰才说性字。此理便与气合了。又曰才是说性。便已兼乎气质。而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又曰成之者性。或昏或明。朱子此个话说。不一而足。不可殚记。而退陶于性圈中。以一性字对举本然及气质。而置之发为情之前。其答奇明彦曰。兼理气有善恶。非但情尔。性亦然矣。大抵吾辈说性。外朱退而为说。则岂说性也哉。朱退之说。已不啻十分可据。而并皆归之记录之误。恐或非尊信之义也。愚于此盖已积受诸公之驳。而思之又思。终不敢苟同于诸公者。以孔子以来旨诀如此。而终有所不敢背之也。此是此学之头颅。而于此不合则便非学也。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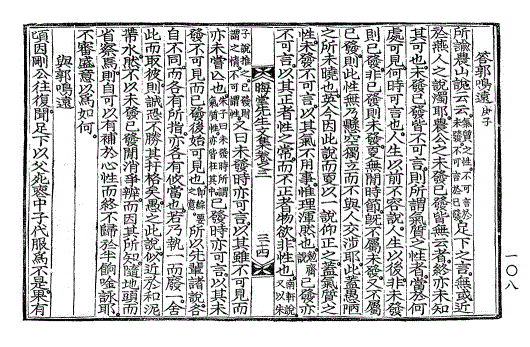 答郭鸣远(庚子)
答郭鸣远(庚子)所谕农山说云云。(气质之性。不可言于未发。不可言于已发。)足下之言。无或近于燕人之说烛耶。农公之未发已发皆无云者。终亦未知其可也。未发已发皆不可言。则所谓气质之性者。当于何处可见。何时可言也。人生以前不容说。人生以后。非未发则已发。非已发则未发。更无閒时节。既不属未发。又不属已发。则此性无乃悬空独立而不与人交涉耶。此盖愚陋之所未晓也。英今因此说而更以一说仰正之。盖气质之性。未发不可言。以其气不用事。惟理浑然也。(勉斋说)已发亦不可言。以其正者性之常。而不正者物欲。非性也。(南轩说。又以朱子说推之。已发则谓之情。不可谓性。)又曰未发时亦可言。以其虽不可见而亦未尝亡也。(朱子曰未发时所谓气质性。亦皆在其中。)已发时亦可言。以其未发不可见而已发后始可见也。(即综要之意。)所以先辈诸说。各自不同。而各有所指。亦各有攸当也。若乃执一而废一。舍此而取彼。则诚恐不胜其捍格矣。愚之此说。似近于和泥带水。然不以未发已发閒消争辨。而因其所知。随地头而省察焉。则自可以有补于心性而终不归于半饷唫咏耶。不审盛意以为如何。
与郭鸣远
顷因刚公往复。闻足下以父死丧中子代服为不是。果有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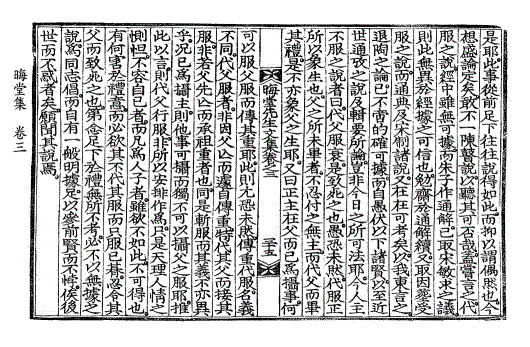 是耶。此事从前足下往往说得如此。而抑以谓偶然也。今想盛论定矣。敢不一陈瞽说。以听其可否哉。盖尝言之。代服之说。经中虽无可据。而朱子作通解。已取宋敏求之议。则此无异于经据之可信也。勉斋于通解续。又取因葬受服之说。而通典及宋制诸说。又在在可考矣。以我东言之。退陶之论。已不啻的确可据。而自愚伏以下诸贤。以至近世通考之说及辑要所论。岂非今日之所可法耶。今人主不服之说者曰。代父服衰。是致死之也。愚恐未然。代服正所以象生也。父之所未毕者。不忍付之无主。而代父而毕其礼。是不亦象父之生耶。又曰正主在父而已为摄事。何可以服父服而传其重耶。此则尤恐未然。传重代服。名义不同。代父服者。非因父亡而遽自传重。特代其父而接其服。非若父先亡而承祖重者也。同是斩服而其义不亦异乎。况己为摄主。则他事可摄而独不可以摄父之服耶。推此以言。则代父行服。非所以安排作为。只是天理人情之恻怛。不容自已者。而凡为人子者。虽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有何害于礼意。而必欲其不代其服而只服己期。忍令其父而致死之也。第念足下于礼无所不考。必不以无据之说。为同志倡。而自有一般明据。足以参前贤而不悖。俟后世而不惑者矣。愿闻其说焉。
是耶。此事从前足下往往说得如此。而抑以谓偶然也。今想盛论定矣。敢不一陈瞽说。以听其可否哉。盖尝言之。代服之说。经中虽无可据。而朱子作通解。已取宋敏求之议。则此无异于经据之可信也。勉斋于通解续。又取因葬受服之说。而通典及宋制诸说。又在在可考矣。以我东言之。退陶之论。已不啻的确可据。而自愚伏以下诸贤。以至近世通考之说及辑要所论。岂非今日之所可法耶。今人主不服之说者曰。代父服衰。是致死之也。愚恐未然。代服正所以象生也。父之所未毕者。不忍付之无主。而代父而毕其礼。是不亦象父之生耶。又曰正主在父而已为摄事。何可以服父服而传其重耶。此则尤恐未然。传重代服。名义不同。代父服者。非因父亡而遽自传重。特代其父而接其服。非若父先亡而承祖重者也。同是斩服而其义不亦异乎。况己为摄主。则他事可摄而独不可以摄父之服耶。推此以言。则代父行服。非所以安排作为。只是天理人情之恻怛。不容自已者。而凡为人子者。虽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有何害于礼意。而必欲其不代其服而只服己期。忍令其父而致死之也。第念足下于礼无所不考。必不以无据之说。为同志倡。而自有一般明据。足以参前贤而不悖。俟后世而不惑者矣。愿闻其说焉。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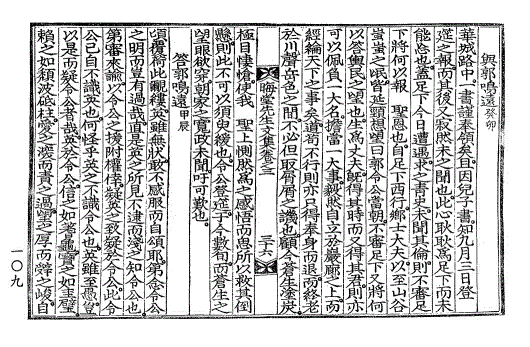 与郭鸣远(癸卯)
与郭鸣远(癸卯)华城路中。一书谨奉领矣。且因儿子书。知九月三日登 筵之报。而其后又寂然未之闻也。此心耿耿为足下而未能忘也。盖足下今日遭遇。求之青史。未闻其伦。则不审足下将何以报 圣恩也。自足下西行。乡士大夫。以至山谷蚩蚩之氓。皆延颈想望曰郭令公当朝。不审足下又将何以答舆民之望也。生为丈夫。既得其时而又得其君。则亦可以佩负一大名。担当一大事。毅然自立于岩廊之上。而经纶天下之事矣。道苟不行则亦只得奉身而退。而终老于川声岳色之间。不必但取屑屑之讥也。顾今苍生涂炭。极目悽怆。使我 圣上恻然为之感悟而思所以救其倒悬。则此不可以须臾缓也。令公登筵。于今数旬。而苍生之望眼欲穿。朝家之宽政未闻。吁可叹也。
答郭鸣远(甲辰)
顷覆荷此覼缕。英虽无状。敢不感服而自颂耶。第念令公之明而岂有过哉。直是英之所见不逮而浅之知令公也。第审来谕。以令公之援附权倖。疑英之致疑于令公。此令公已自不识英也。何怪乎英之不识令公也。英虽至愚。岂以是而疑令公者哉。英于令公。信之如蓍龟。宝之如圭璧。赖之如颓波砥柱。爱之深而责之过。望之厚而辞之峻。自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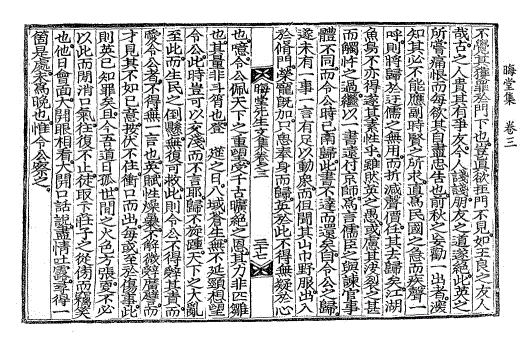 不觉其获罪于门下也。岂真欲拒门不见。如王良之友人哉。古之人贵其有争友。今人諓諓。朋友之道遂绝。此英之所尝痛恨而每欲其自尽忠告也。前秋之妄劝一出者。深知其必不能应副时贤之所求。直为民国之急而疾声一呼。则将归于迂儒之无用。而折减声价。任其去归矣。江湖鱼鸟不亦得遂其素性乎。虽然英之愚。或虑其决裂之甚而触忤之过。继以一书远付京师。为言儒臣之与谏官事体不同。而令公时已南归。此书不达而还矣。自令公之归。遂未有一事一言有足以动众。而但闻其山巾野服。出入于脩门。荣宠既加。只思奉身而归。英于此不得无疑于心也。噫。令公佩天下之重望。受千古旷绝之恩。其力非匹雏也。其量非斗筲也。登 筵之日。八域苍生。无不延颈想望令公。此时岂可以交浅而不言耶。归不旋踵。天下之大乱至此。而生民之倒悬。无复可救。此则令公不得辞其责。而爱令公者。不得无一言也。英赋性燥㬥。不解微辞广譬。而才见其不如己意。按伏不住。冲口而出。每或至于伤事。此则英已知罪矣。且今吾道日孤。世间之火色方张。更不必以此而閒消口气。往复不止。徒取卞庄子之从傍而窃笑也。他日会面。大开眼相看。大开口话说。尽情吐露。寻得一个是处。未为晚也。惟令公察之。
不觉其获罪于门下也。岂真欲拒门不见。如王良之友人哉。古之人贵其有争友。今人諓諓。朋友之道遂绝。此英之所尝痛恨而每欲其自尽忠告也。前秋之妄劝一出者。深知其必不能应副时贤之所求。直为民国之急而疾声一呼。则将归于迂儒之无用。而折减声价。任其去归矣。江湖鱼鸟不亦得遂其素性乎。虽然英之愚。或虑其决裂之甚而触忤之过。继以一书远付京师。为言儒臣之与谏官事体不同。而令公时已南归。此书不达而还矣。自令公之归。遂未有一事一言有足以动众。而但闻其山巾野服。出入于脩门。荣宠既加。只思奉身而归。英于此不得无疑于心也。噫。令公佩天下之重望。受千古旷绝之恩。其力非匹雏也。其量非斗筲也。登 筵之日。八域苍生。无不延颈想望令公。此时岂可以交浅而不言耶。归不旋踵。天下之大乱至此。而生民之倒悬。无复可救。此则令公不得辞其责。而爱令公者。不得无一言也。英赋性燥㬥。不解微辞广譬。而才见其不如己意。按伏不住。冲口而出。每或至于伤事。此则英已知罪矣。且今吾道日孤。世间之火色方张。更不必以此而閒消口气。往复不止。徒取卞庄子之从傍而窃笑也。他日会面。大开眼相看。大开口话说。尽情吐露。寻得一个是处。未为晚也。惟令公察之。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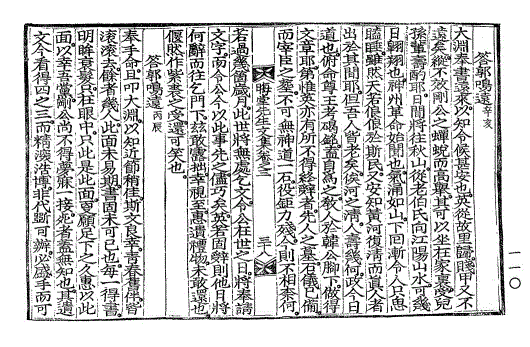 答郭鸣远(辛亥)
答郭鸣远(辛亥)大渊奉书远来。以知令候甚安也。英从故里归。贱甲又不远矣。纵不效刚公之蝉蜕而高举。其可以坐在家里。受儿孙辈寿酌耶。日间将往秋山。从老伯氏向江阳山水。可几日翱翔也。神州革命始闻也。气涌如山。下回渐令人只思瞌睡。虽然天若俍俍于斯民。又安知黄河复清而真人者出于其间耶。但吾人皆老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政今日道也。俯命尊王考碣铭。盍自为之。教人于韩公脚下。做得文章耶。第惟英亦有所不得终辞者。先人之墓。石仪已备。而宰臣之葬。不可无神道一石。役钜力残。今则不相柰何。若过几个岁月。此世将无处乞文。令公在世之日。将奉请文字。而令公今以此事先之。尽巧矣。英若固辞则他日将何辞而往乞门下。玆敢露拙。幸视至。惠遗礼物。未敢还也。偃然作紫裘之受。还可笑也。
答郭鸣远(丙辰)
奉手命。且叩大渊。以知近节稍佳。斯文良幸。青春旧伴。皆滚滚去。馀者几人。此面未易期。书固未可已也。每一得书。明眸衰发。只在眼中。只此是此面。更愿足下之久惠以此面。以幸吾党。刚公尚不得梦寐一接。死者盖无知也。其遗文今看得四之三。而精深浩博。非代斲可办。必盛手而可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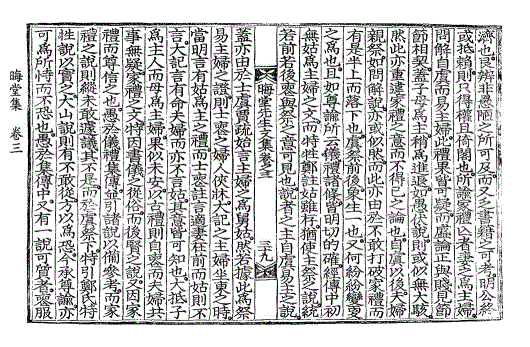 济也。艮辨非愚陋之所可及。而又乏书籍之可考。明公终或抵赖。则只得权且倚阁也。所谕家礼亡者妻之为主妇。问解自虞而易主妇。此礼果皆可疑。而盛论正与贱见节节相契。盖子母为主。稍为进退。如愚伏说。则或似无大骇。然此亦重违家礼之意而不得已之论也。自虞以后。夫妇亲祭。如问解说。亦或似然。而此亦由于不敢打破家礼而有是半上而落下也。虞祭前后。象生一也。又何纷纷变更之为也。且如尊谕所云仪礼诸条。皆明切的确。经传中初无姑为主妇之文。而特牲郑注姑虽存。犹使主祭之说。统若前若后丧与祭之意可见也。说者之主自虞易主之说。盖亦由于士虞贾疏始言主妇之为舅姑。然若据此为祭易主妇之證。则士丧之妇人侠床。大记之主妇坐东之时。当明言有姑为主之礼。而士丧注言适妻在前而姑则不言。大记言有命夫妇而亦不言姑。其意皆可知也。大抵子为主人而母为主妇。果似未安。以古礼则自丧而夫妇共事无疑。家礼之文。特因书仪之从俗。而后贤之说。又因家礼而尊信之也。愚于仪礼集传。并引诸说以备参考。而家礼之说则纵未敢遽议其不是。而于虞祭下。特引郑氏特牲说以实之。大山说则有不敢从。方以为恐。今承尊谕。亦可为所恃而不恐也。愚于集传中。又有一说可质者。丧服
济也。艮辨非愚陋之所可及。而又乏书籍之可考。明公终或抵赖。则只得权且倚阁也。所谕家礼亡者妻之为主妇。问解自虞而易主妇。此礼果皆可疑。而盛论正与贱见节节相契。盖子母为主。稍为进退。如愚伏说。则或似无大骇。然此亦重违家礼之意而不得已之论也。自虞以后。夫妇亲祭。如问解说。亦或似然。而此亦由于不敢打破家礼而有是半上而落下也。虞祭前后。象生一也。又何纷纷变更之为也。且如尊谕所云仪礼诸条。皆明切的确。经传中初无姑为主妇之文。而特牲郑注姑虽存。犹使主祭之说。统若前若后丧与祭之意可见也。说者之主自虞易主之说。盖亦由于士虞贾疏始言主妇之为舅姑。然若据此为祭易主妇之證。则士丧之妇人侠床。大记之主妇坐东之时。当明言有姑为主之礼。而士丧注言适妻在前而姑则不言。大记言有命夫妇而亦不言姑。其意皆可知也。大抵子为主人而母为主妇。果似未安。以古礼则自丧而夫妇共事无疑。家礼之文。特因书仪之从俗。而后贤之说。又因家礼而尊信之也。愚于仪礼集传。并引诸说以备参考。而家礼之说则纵未敢遽议其不是。而于虞祭下。特引郑氏特牲说以实之。大山说则有不敢从。方以为恐。今承尊谕。亦可为所恃而不恐也。愚于集传中。又有一说可质者。丧服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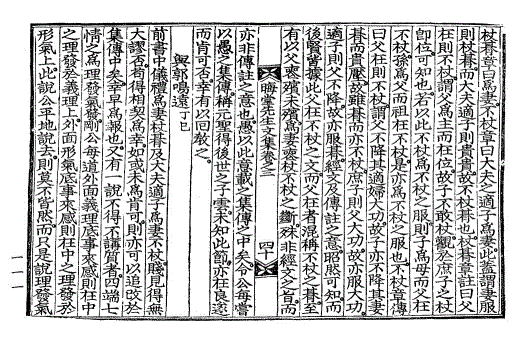 杖期章曰为妻。不杖章曰大夫之适子为妻。此盖谓妻服则杖期。而大夫适子则贵贵。故不杖期也。杖期章注曰父在则不杖。谓父为主而在位。故子不敢杖。观于庶子之杖即位。可知也。若以此不杖为不杖之服。则子为母而父在不杖。孙为父而祖在不杖。是亦为不杖之服也。不杖章传曰父在则不杖。谓父不降其适妇大功。故子亦不降其妻期而贵压。故虽期而亦不杖。庶子则父大功。故亦服大功。适子则父不降。故亦服期。经文及传注之意。昭然可知。而后贤皆据此父在不杖之文。而父在者混称不杖之期。至有以父丧殡未殡。为妻丧杖不杖之断。殊非经文之旨。而亦非传注之意也。愚以此意载之集传之中矣。令公每尝以愚之集传。称元圣得后世之子云。未知此节。亦在良遂而肯可否。幸有以回教之。
杖期章曰为妻。不杖章曰大夫之适子为妻。此盖谓妻服则杖期。而大夫适子则贵贵。故不杖期也。杖期章注曰父在则不杖。谓父为主而在位。故子不敢杖。观于庶子之杖即位。可知也。若以此不杖为不杖之服。则子为母而父在不杖。孙为父而祖在不杖。是亦为不杖之服也。不杖章传曰父在则不杖。谓父不降其适妇大功。故子亦不降其妻期而贵压。故虽期而亦不杖。庶子则父大功。故亦服大功。适子则父不降。故亦服期。经文及传注之意。昭然可知。而后贤皆据此父在不杖之文。而父在者混称不杖之期。至有以父丧殡未殡。为妻丧杖不杖之断。殊非经文之旨。而亦非传注之意也。愚以此意载之集传之中矣。令公每尝以愚之集传。称元圣得后世之子云。未知此节。亦在良遂而肯可否。幸有以回教之。与郭鸣远(丁巳)
前书中仪礼为妻杖期及大夫适子为妻不杖。贱见得无大谬否。苟得相契为幸。如或未为肯可。则亦可以追改于集传中矣。幸早为报也。又有一说不得不讲质者。四端七情之为理发气发。刚公每道外面义理底事来感则在中之理发于义理上。外面形气底事来感则在中之理发于形气上。此说公平地说去。则莫不皆然。而只是说理发气
晦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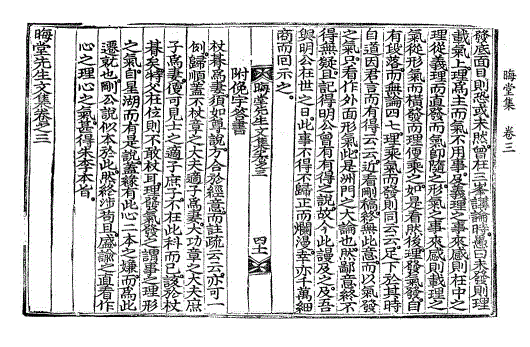 发底面目则恐或未然。曾在三峰讲论时。愚曰未发则理载气上。理为主而气不用事。及义理之事来感则在中之理从义理而直发而气即随之。形气之事来感则载理之气从形气而横发而理便乘之。如是看然后。理发气发。自有段落。而无论四七。理乘气而发则同云云。足下于其时自道因君言而有得云云。近看刚稿。终无此意。而以气发之气。只看作外面形气。此是洲门之大论也。然鄙意终不得无疑。且记得明公曾有有得之说。故今此谩及之。及吾与明公在世之日。此事不得不归正而烂漫。幸亦千万细商而回示之。
发底面目则恐或未然。曾在三峰讲论时。愚曰未发则理载气上。理为主而气不用事。及义理之事来感则在中之理从义理而直发而气即随之。形气之事来感则载理之气从形气而横发而理便乘之。如是看然后。理发气发。自有段落。而无论四七。理乘气而发则同云云。足下于其时自道因君言而有得云云。近看刚稿。终无此意。而以气发之气。只看作外面形气。此是洲门之大论也。然鄙意终不得无疑。且记得明公曾有有得之说。故今此谩及之。及吾与明公在世之日。此事不得不归正而烂漫。幸亦千万细商而回示之。附俛宇答书[郭钟锡]
杖期为妻。须如尊说。方合于经意。而注疏云云。亦可一例。归顺盖不杖章之大夫适子为妻。大功章之大夫庶子为妻。便可见士之适子庶子。不在此科而已。该于杖期矣。特父在位则不敢杖耳。理发气发之谓事之理形之气。自星湖而有是说。盖缘有此心二本之嫌。而为此迁就也。刚公说似本于此。然终涉苟且。盛谕之直看作心之理心之气。甚得朱李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