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x 页
响山文集卷之八
杂著
杂著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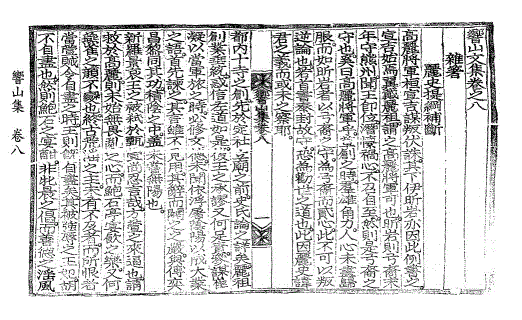 丽史提纲补断
丽史提纲补断高丽将军桓宣吉谋叛伏诛。其下伊昕岩亦因此例书之。宣吉始焉翼戴丽祖。谓之高丽将军可也。昕岩则弓裔末年守熊州。闻王即位。潜怀祸心。不召自至。然则是弓裔之守也。奚曰高丽将军乎。草创之时。群雄角力。人心未尽归服。而如昕岩者以弓裔之守。为弓裔而贰心。此不可以叛逆论也。若首书泰封故守。恐为劝世之道也。此因丽史讳君之义而或未之察耶。
都内十寺之创。先于定社立庙之前。史氏论之详矣。丽祖创业垂统。惑信左道如是。后王之承谬又何足责。参谋崔凝以当军旅之时。必修文德。未闻依浮屠阴阳以成大业之语。首先谏之。其言虽不见用。其辞而辟之之严。与傅奕昌黎同其功。积阴之中。盖未尝无阳也。
新罗景哀王之被弑于甄萱尚忍言哉。方萱之来逼也。请救于高丽。则未始无畏乱之心。而鲍石亭宴饮之乐。又何燕雀之颜不变也。终古荒淫之主。未有不及者。而所恨者当萱贼令自尽之时。王则既自尽矣。其被强辱之王妃。胡不自尽也。然则鲍石之宴酣。非牝晨之倡。而善德之淫风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5L 页
 有自来者欤。其不愧于弓裔之夫人乎。
有自来者欤。其不愧于弓裔之夫人乎。甄萱与丽祖交致书也。萱曰邦君薨变。遂奉景明王之表弟劝即尊位。再造危邦。丧君有君。丽祖曰仗义尊周。谁似桓文。乘间谋汉。惟看莽卓。又曰庶效鹰鹯之逐。以申犬马之勤。盖甄萱罗之反贼也。丽祖罗之善邻也。甄萱弑景明而讳之曰薨变则是尚知得罪于伦常也。丽祖尚称尊周之义而数萱以莽卓。则是如鄢郢之役。责昭王之不返包茅之不供而义理立于天下也。义理既立则天人必与。义理既失。天人必诛。此萱所以亡而丽所以兴也。
神剑杀弟囚父而自立。天下之乱臣贼子孰有甚于此者乎。丽祖之讨神剑。盖因其父萱之请。则既讨之后。不杀而反赐之官何哉。以是之故。萱发疽而死。其死也果孰使之然哉。举义声罪。为其蔑天伦也。而终令天伦倒丧。其何以惧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乎。郑仲夫,金镛之辈接迹于末年者。无乃立法之一失欤。
王规欲立其外孙。谮尧昭于惠宗。小人之常情也。惠宗知其诬而妻昭以长女。以强昭之势。其不信谮固为明也。然立国之初。首犯不娶同姓之戒。以开家法之不正。宁不可惜乎。穴壁谋弑之时。不即诛规而乃待平壤卫兵之至。则其间朴大匡述熙已被规之擅杀。大匡之死不亦冤乎。以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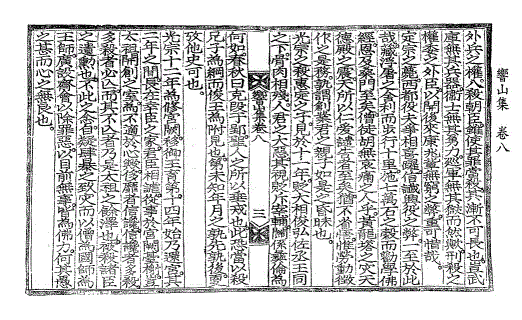 外兵之权。入杀朝臣。虽使其罪当杀。其渐不可长也。岂武库无其兵器。卫士无其勇力。巡军无其狱而然欤。刑杀之权委之外臣。以开后来康兆辈无穷之弊。重可惜哉。
外兵之权。入杀朝臣。虽使其罪当杀。其渐不可长也。岂武库无其兵器。卫士无其勇力。巡军无其狱而然欤。刑杀之权委之外臣。以开后来康兆辈无穷之弊。重可惜哉。定宗之薨。西都役夫争相喜跃。信谶兴役之弊。一至于此哉。藏浮屠之舍利而步行十里。施七万石之谷而劝学佛经。恩及桑门至矣。僧徒胡无哀痛之人乎。黄龙塔之灾天德殿之震。天所以仁爱谴告者至矣。犹不省悟。惟劳动徵作之是务。孰谓创业君之亲子如是之昏昧也。
光宗之杀惠定之子。见于十一年。贬大相俊弘佐丞王同之下。骨肉相残。人君之大恶。其视贬斥宰辅。关系彝伦为何如。春秋曰克段于郢。圣人之所以垂戒也。此恐当以杀兄子为纲而俊王为附见也。第未知年月之孰先孰后。更考他史可也。
光宗十二年为修宫阙。移御王育第。十四年始乃还宫。其二年之间。长在幸臣之家。君臣相谑。从事于宫阙台榭。岂太祖开创之室。为不适于心欤。侈靡者信谗。信谗者多杀。多杀者必亡。而其不亡者乃是太祖之馀泽也。被杀诸臣之遗勋也。不此之念。自疑肆暴之致灾而以僧为国师为王师。广设齐会以除罪恶。以目前无事。皆为佛力。何其愚之甚而心之无良也。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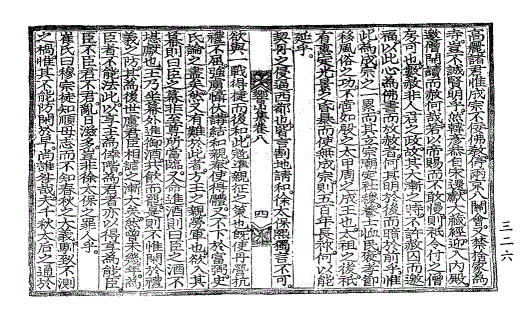 高丽诸君惟成宗不佞佛教。停两京八关会。又禁舍家为寺。岂不诚贤明乎。然韩彦恭自宋还。献大藏经。迎入内殿。邀僧开读而赦何哉。若以帝赐而不敢慢。则祇令付之僧房可也。数赦非人君之政。故其大渐之时。不许赦囚而邀福。以此心为佛书而放赦者。何其明于后而暗于前乎。惟此为成宗之一累。而其立宗庙定社稷。养士恤民。褒孝节移风俗之功。不啻如殷之太甲周之成王也。太祖之后。祇有惠定光景之昏暴而使无成宗。则五百年长祚。何以能延乎。
高丽诸君惟成宗不佞佛教。停两京八关会。又禁舍家为寺。岂不诚贤明乎。然韩彦恭自宋还。献大藏经。迎入内殿。邀僧开读而赦何哉。若以帝赐而不敢慢。则祇令付之僧房可也。数赦非人君之政。故其大渐之时。不许赦囚而邀福。以此心为佛书而放赦者。何其明于后而暗于前乎。惟此为成宗之一累。而其立宗庙定社稷。养士恤民。褒孝节移风俗之功。不啻如殷之太甲周之成王也。太祖之后。祇有惠定光景之昏暴而使无成宗。则五百年长祚。何以能延乎。契丹之侵逼西都也。皆言割地请和。徐太保熙独言不可。欲与一战得捷而后和。此寇准亲征之策也。既使丹营抗礼不屈。强虏慑伏。讲结和亲。奉使得体。又不下于富弼。史氏论之尽矣。然又有难于此者。方王之亲劳军也。欲入其幕则曰臣之幕非至尊所当临。又命进酒则曰臣之酒不堪献也。王乃坐幕外进御酒。共饮而罢。是则不惟闲于礼义之防。其为后世虑君臣相谑之渐大矣。然曾未几年。为臣者不能法此。以享王为倖阶。为君者亦以得享为能臣。臣不臣君不君。乱日滋多。岂非徐太保之罪人乎。
崔氏曰穆宗徒知顺母志而不知春秋之大义。驯致不测之祸。惟其不能防闲于早。尚谁咎哉。夫千秋太后之通于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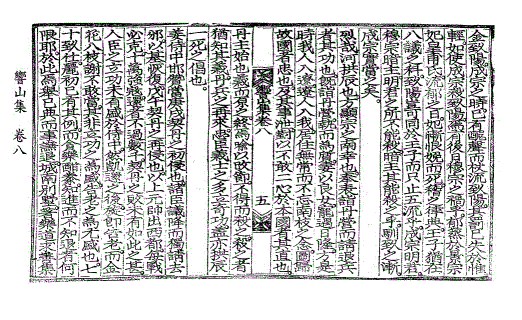 金致阳。成宗之时。已有丑声而杖流致阳。其罚已失于惟轻。如使成宗杀致阳。焉有后日穆宗之祸乎。郁蒸于景宗妃皇甫氏。流郁之日。妃惭恨娩而死。稽之律典。王子犹在八议之科。致阳岂可同于王子而只止五流乎。成宗明君。穆宗暗主。明君之所不能杀。暗主其能杀之乎。驯致之渐。成宗实当之矣。
金致阳。成宗之时。已有丑声而杖流致阳。其罚已失于惟轻。如使成宗杀致阳。焉有后日穆宗之祸乎。郁蒸于景宗妃皇甫氏。流郁之日。妃惭恨娩而死。稽之律典。王子犹在八议之科。致阳岂可同于王子而只止五流乎。成宗明君。穆宗暗主。明君之所不能杀。暗主其能杀之乎。驯致之渐。成宗实当之矣。烈哉河拱辰也。方显宗之南幸也。奉表诣丹营而请退兵者其功也。既诣丹营。执而为质。妻以良女。宠遇日隆。方是时我人入辽。辽人入我。居住无常而不忘南枝之念。图归故国者忠也。及其事泄。对以不敢二心于本国者其直也。丹主始也义而原之。终焉喻以改节。不得而杀之。杀之者犹知其义。丹兵之再来。忠臣义士之多立奇功。盖亦拱辰一死之倡也。
姜侍中邯赞当庚戌契丹之初侵也。诸臣议降而独请去邠。以基恢复。戊午契丹之再侵也。以上元帅出西都。每战必克。十万强寇。还者不过数千。契丹之败未有如此之甚。人臣之立功未有盛于侍中。然凯还之后。旋即告老。而金花八枝谢不敢当。其非立功之为盛。告老之为尤盛也。七十致仕。丽初已有其例。而贪乐酣豢。知进而不知退者何限耶。于此焉举已典而事谦退。城南别墅。著乐道求善集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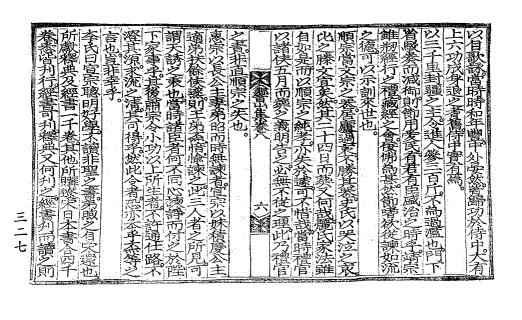 以自歌咏。当时时和年丰。中外晏然。皆归功于侍中。大有上六功成身退之耆旧。侍中实有焉。
以自歌咏。当时时和年丰。中外晏然。皆归功于侍中。大有上六功成身退之耆旧。侍中实有焉。以三千里封疆之主。令进人蔘三百斤。不为过滥也。门下省驳奏而减御。则节用爱民。有君有臣盛治之时乎。靖宗虽刱经行之礼。藏经之会。佞佛为甚。然节嗜欲从谏如流之德。可以示训来世也。
顺宗当文宗之丧。居庐过哀。不胜其丧。史氏以哭泣之哀。比之滕文宜矣。然其二十四日而葬又何哉。丽氏家法虽自如是。而以顺宗之纯孝。亦失于遽。可不惜哉。当时礼官以诸侯五月而葬之义明告之。必无不从之理。此乃礼官之责。非直顺宗之失也。
惠宗以长公主妻弟昭而时无谏者。宣宗以妹积庆公主适弟扶馀侯燧。则王弟
李氏曰宣宗聪明好学。不读非圣之书。弟煦之自宋还也。所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其他所购辽宋日本书合四千卷。悉皆刊行。经书可刊。释典又何刊之。经书刊而读之则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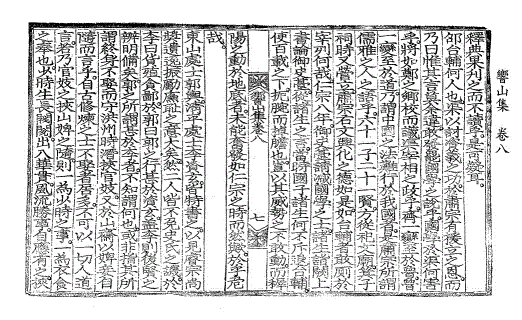 释典果刊之而不读乎。是可疑耳。
释典果刊之而不读乎。是可疑耳。邵台辅何人也。渠以讨资义之功。于肃宗有援立之恩。而乃曰惟其言莫余违。敢发罢国学之说乎。国学于渠何害乎。将如郑之乡校而议渠宰相之政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乃谓中国之法难行于我国者。是肃宗所谓儒雅之人之语乎。六十一子二十一贤。方从祀文庙。箕子祠时又营立。肃宗右文兴化之德如是。如台辅者敢厕于宰列何哉。仁宗八年。御史台请减国学之士。诸生诣阙上书论御史台。从诸生之言。当时国子诸生何不斥退台辅。使百载之下。扼腕而掉胆也。岂以其威势之不敢动。而稚阳之动于地底者。未能奋发如仁宗之时而然欤。于乎危哉。
东山处士郭舆。清平处士李资玄。皆特书之。以见睿宗尚奖遗逸振励廉耻之意大矣。然二人皆不免史氏之讥。于李曰货殖贪鄙。于郭曰郭之行甚于资玄。盖李则后贤之辨明备矣。郭之所谓甚于李者。不知谓何也。或非指其所谓终身不娶而守洪州时潜挟官妓。又于山斋以婢妾自随而言乎。自古修炼之士不娶者居多。不可以一切人道言。若乃官妓之挟山婢之随。则一为少时之事。一为衣食之奉也。少时生长阀阅。出入华贯。风流胜事。自应有之。挟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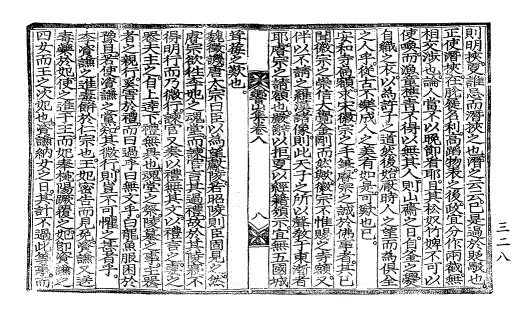 则明挟。更谁忌而潜挟之也。潜之云云。已是过于贬驳也。正使潜挟。在脱屣名利。高蹈物表之后。政宜分作两截。无相交涉也。论人当不以晚节看耶。且其松奴竹婢不可以使唤。而渔童樵青不得以无其人。则山斋之日。自釜之爨自织之衣。以为许子之道然后。始厌时人之望而为俱全之人乎。从古不乐成人之美有如是。可叹也已。
则明挟。更谁忌而潜挟之也。潜之云云。已是过于贬驳也。正使潜挟。在脱屣名利。高蹈物表之后。政宜分作两截。无相交涉也。论人当不以晚节看耶。且其松奴竹婢不可以使唤。而渔童樵青不得以无其人。则山斋之日。自釜之爨自织之衣。以为许子之道然后。始厌时人之望而为俱全之人乎。从古不乐成人之美有如是。可叹也已。安和寺扁额。求宋徽宗之手笔。睿宗之诚于佛事者。其已闻徽宗之崇信大觉金刚而然欤。徽宗不惟赐之寺额。又伴以不请之罗汉诸像。则此天子之所以声教于东渐者耶。睿宗之请额也。严辞以拒。更以经籍颁示。宜无五国城茸莓之叹也。
魏徵讥唐太宗曰臣以为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然睿宗欲往李妃之魂堂。而谏官言其过礼。故于其陵寝不得明行而乃微行。谏官又奏以礼无其文。以礼言之。妻之丧夫主之。自上达下。礼无异也。魂堂之祭。陵墓之事。主丧者之亲行。奚害于礼。而曰过乎曰无文乎。白龙鱼服困于豫且。若使资谦之党。知其微行。则岂不可惧之甚者乎。
李资谦之进毒饼于仁宗也。王妃密告而见免。资谦又送毒药于妃。使之进于王。而妃奉碗阳蹶覆之。妃即资谦之四女而王之次妃也。资谦纳女之日。其计不过此等事。而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9H 页
 为其女者犹知其父之稔恶。而明于适人从夫之义。再毒而再免之。不亦贤矣哉。及资谦之谋乱而议律也。以极逆之女。不可奉承至尊废之。于义固当然。资谦既失轻典而不诛。则仁宗不以极逆待资谦也。于其台谏之请废妃也。何不念潜救之事。而无难于割恩乎。是或资谦之三女又为元妃。而两女之中。不可分其恩不恩。故并废之耶。若论次妃之功。当在拓俊京自新效力之先也。此明宗所以葬以后礼。而不忘仁宗之遗意也。
为其女者犹知其父之稔恶。而明于适人从夫之义。再毒而再免之。不亦贤矣哉。及资谦之谋乱而议律也。以极逆之女。不可奉承至尊废之。于义固当然。资谦既失轻典而不诛。则仁宗不以极逆待资谦也。于其台谏之请废妃也。何不念潜救之事。而无难于割恩乎。是或资谦之三女又为元妃。而两女之中。不可分其恩不恩。故并废之耶。若论次妃之功。当在拓俊京自新效力之先也。此明宗所以葬以后礼。而不忘仁宗之遗意也。辽金近而汴临安远。其势不得不厚近而简远也。然其心悦诚服则未尝无内华外夷之分。徽宗之末。睿宗请内医二人密告曰朝廷用兵于辽。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捍。女真虎狼不可友也。又指授阵法。章蔡辈闻之。置毒食中。杀其二医。如使医不见杀。徽宗用其计。必无北狩之患也。此非内华外夷之心也耶。高宗南渡。即周平之东迁也。王业一脉。不绝如缕。遣使欲假道如金。仁宗虽不许。然旋为报聘。又逐年执壤。故宋使之来。乃曰中原多事。驻驾江湖。使之姑停聘问。上下之交相爱而恩礼之隆厚有若是矣。金人未始不知宋使之往来而不执言者。亦以旧君之不忍忘而侯度之为可尚故也。若复置二心于兴衰之间。而为凉煖之情于尊攘之地。则仁宗安得为仁宗也。此可为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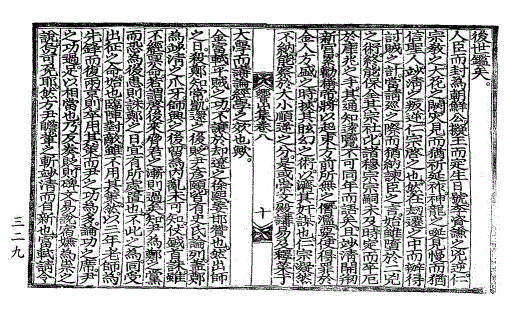 后世鉴矣。
后世鉴矣。人臣而封为朝鲜公。拟王而定生日号。李资谦之凶逆。仁宗教之。大花之阙灾见而犹祈延祚。神龙之唌见慢而犹信圣人。妙清之叛逆。仁宗启之也。然在劫迁之中而办得讨贼之计。当请巡之际而犹纳谏臣之言。始虽堕于二凶之术。终能保全其宗社。比诸穆宗宗嗣未及时定而卒厄于康兆之手。其通知远览。不可同年而语矣。且妙清开刱新宫。累劝称帝。将以起东方前所无之僭滥。要使得罪于金人方盛之时。挟其眩幻之术。以济其奸谋也。仁宗凝然不纳。能察于大小顺逆之分。是或崇文殿讲易及释菜于大学而讲论经学之效也欤。
金富轼平贼之功。不让于却辽之徐熙,姜邯赞也。然出师之日。杀郑知常。凯还之后。贬尹彦颐。皆有史氏论列。盖郑为妙清之爪牙。师兴之后。留为内乱未可知。仗钺首诛。虽不经禀命。若谓启后来胁君之渐则过矣。知尹为郑之党而恐为后患则诛郑之日。宜有所处置也。不此之为。同受出征之命。始也临阵对敌。虽不用其策。然以三年老师。为先锋而复两京。则卒用其策而尹之功为多。论功之席。尹之功过。足以相当也。乃反奏贬。则碑文易说宿嫌为祟之说。乌可免耶。然方尹瞻辈之斩妙清而自新也。富轼请令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0H 页
 两府贳罪。两府不听而囚之。赵匡因以更反。其始诛郑之日。不连坐彦颐者。为其多杀贼党。恐令反侧者不安而许其自新之路。亦如欲优容于尹瞻者耶。贼既平矣。若不论前过则又恐难以惩后。所以不得已贬黜之。亦如拓俊京讨资谦之功。难掩与资谦之罪。故因台论而流之者耶。不然以富轼之达识忠谠。措置政事者。公耳国耳。无一苟且。区区睚眦之怨。岂以君子而必报乎。是不可知也。
两府贳罪。两府不听而囚之。赵匡因以更反。其始诛郑之日。不连坐彦颐者。为其多杀贼党。恐令反侧者不安而许其自新之路。亦如欲优容于尹瞻者耶。贼既平矣。若不论前过则又恐难以惩后。所以不得已贬黜之。亦如拓俊京讨资谦之功。难掩与资谦之罪。故因台论而流之者耶。不然以富轼之达识忠谠。措置政事者。公耳国耳。无一苟且。区区睚眦之怨。岂以君子而必报乎。是不可知也。天可谌乎。不可谌乎。毅宗以太后之始欲立次子。语侵太后。太后仰天而誓。䨓震殿柱。是天可谌也。及其尊信图谶。迁母后而流弟。暻天于是时。当震而不震。是天不可谌也。然其所谓图谶者。实在其弟翼阳侯皓。皓即明宗也。天若于是时又震之。则将不疑暻而疑皓。皓将危矣。天将保皓而不震欤。迁母流弟之恶不悛。而终入于庆州大釜之中。天之震无有大于此者。天非可谌者乎。
指蓬艾为瑞草。水鸟为玄鹤。狼星为寿星。此惑于嘉祥也。庆明之宫。犯吠犬之头。白州之殿。值客虎之方。此侈于峻宇也。郑諴以宦者列宰枢。无比以宫人市货赂。自制贺表而示近臣。恶庭诤而使勿言事。如此而焉有不亡之君乎。终古兴君。其治也不谋而同。亡君其政也亦不约而同。丽氏有毅宗。其周之幽厉宋之徽钦也欤。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0L 页
 国之有文武臣。文以辅君德而出治道。武以仗兵威而平邦国。在辅导之地。全以谗邪奸佞。陷君于辛受之域。在兵威之地。全以猜憝觊觎而自纳于莽卓之科。人人得以诛之也。于乎。普贤院之变。实文臣之自速也。未全武臣之罪也。毅宗轻佻辩慧。淫荡侈靡。无恶不具。然观于獭岭路上。追念郑袭明若在。吾岂至此之说。则所谓汾水之悔心也。如使金諹,文克谦诸人更申前日之请而罢黜奸宵则宜无不从之理也。普贤之变。何从而生乎。被杀之中李复基,林宗植,韩赖之辈。于渠何责。惟金敦中以富轼之子。薄有文艺。岂不观于其父所撰三国史耶。国之将亡也。必有奸臣导之以谗邪也。何不殷鉴而全为谗邪之道。自速其身诛而君弑乎。郑仲夫之凶恶。始自擅开北门之时。则其羸豕之躅。莫可御也。然燃须之憾。实自敦中发之。大夫骄人则失其家。非敦中之谓乎。太甲不放。不能克终允德。昌邑不废。不能保有汉业。使毅宗不废。亦不可保有丽祚矣。然于其废之也。有伊尹之志则可。自霍光以下。妻子已及于乱。况以仲夫之恶。全出猜憾。恣行废弑。多杀无罪者。宁有逭于天诛之理哉。
国之有文武臣。文以辅君德而出治道。武以仗兵威而平邦国。在辅导之地。全以谗邪奸佞。陷君于辛受之域。在兵威之地。全以猜憝觊觎而自纳于莽卓之科。人人得以诛之也。于乎。普贤院之变。实文臣之自速也。未全武臣之罪也。毅宗轻佻辩慧。淫荡侈靡。无恶不具。然观于獭岭路上。追念郑袭明若在。吾岂至此之说。则所谓汾水之悔心也。如使金諹,文克谦诸人更申前日之请而罢黜奸宵则宜无不从之理也。普贤之变。何从而生乎。被杀之中李复基,林宗植,韩赖之辈。于渠何责。惟金敦中以富轼之子。薄有文艺。岂不观于其父所撰三国史耶。国之将亡也。必有奸臣导之以谗邪也。何不殷鉴而全为谗邪之道。自速其身诛而君弑乎。郑仲夫之凶恶。始自擅开北门之时。则其羸豕之躅。莫可御也。然燃须之憾。实自敦中发之。大夫骄人则失其家。非敦中之谓乎。太甲不放。不能克终允德。昌邑不废。不能保有汉业。使毅宗不废。亦不可保有丽祚矣。然于其废之也。有伊尹之志则可。自霍光以下。妻子已及于乱。况以仲夫之恶。全出猜憾。恣行废弑。多杀无罪者。宁有逭于天诛之理哉。弑君之贼。人得以诛之。大义既立。名以讨贼。不论其事之成败。皆可谓之忠义也。金甫当,赵位宠皆为毅宗兴兵。不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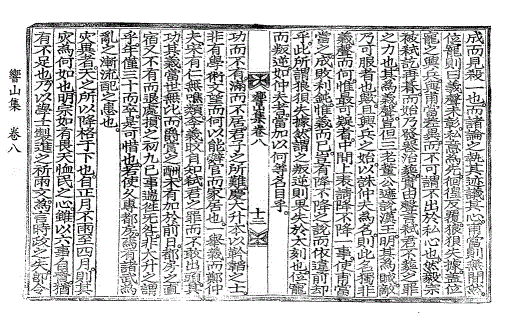 成而见杀一也。而诸论之执其迹议其心。甫当则无间然。位宠则曰义声未彰。私意为先。徊徨反覆。狼狈失据。盖位宠之兴兵。与甫当差异。而不可谓不出于私心也。然毅宗被弑讫再期。而始乃发丧治葬。实由声言弑君不葬之罪之力也。其为义声。岂但三老蕫公遮说汉王。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者也欤。且兴兵之始。以诛仲夫为名。则此名独非义声而何。惟最可疑者。中间上表请降不降一事。使甫当当之。成败利钝。惟义而已。岂有降不降之说而依违前却乎。此所谓狼狈失据。然谓之叛逆则果失于太刻也。位宠而叛逆。如仲夫者。当加以何等名目乎。
成而见杀一也。而诸论之执其迹议其心。甫当则无间然。位宠则曰义声未彰。私意为先。徊徨反覆。狼狈失据。盖位宠之兴兵。与甫当差异。而不可谓不出于私心也。然毅宗被弑讫再期。而始乃发丧治葬。实由声言弑君不葬之罪之力也。其为义声。岂但三老蕫公遮说汉王。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者也欤。且兴兵之始。以诛仲夫为名。则此名独非义声而何。惟最可疑者。中间上表请降不降一事。使甫当当之。成败利钝。惟义而已。岂有降不降之说而依违前却乎。此所谓狼狈失据。然谓之叛逆则果失于太刻也。位宠而叛逆。如仲夫者。当加以何等名目乎。功而不有。满而不居。君子之所难。庆大升本以靲韬之士。非有学术文望而何以能辞官而家居也。一举义而郑仲夫,宋有仁无噍类。李义旼自知弑君之罪而不敢出头。其功其义当世无比。而爵赏之酬。未有加于前日。都房之直宿又不有而退处。损之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非大升之谓乎。年仅三十而卒。是可惜也。若使久专都房。焉有诸武为乱之渐流配之患也。
灾异者。天之所以降格于下也。自正月不雨至四月。则其灾为何如也。明宗如有畏天恤民之心。虽以六事自责。犹有不足也。乃以学士制进之祈雨文。为言时政之失。即令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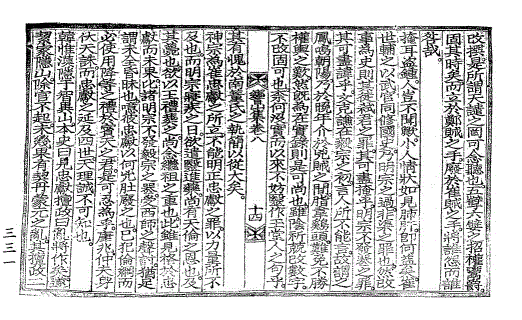 改撰。是所谓天谴之罔可念听也。五孽六嬖之招权鬻爵。固其时矣。而立于郑贼之手。废于崔贼之手。将谁怨而谁咎哉。
改撰。是所谓天谴之罔可念听也。五孽六嬖之招权鬻爵。固其时矣。而立于郑贼之手。废于崔贼之手。将谁怨而谁咎哉。掩耳盗钟。人岂不闻欤。小人情状。如见肺肝。即何益矣。崔世辅之以武官同修国史。乃明宗之过。非渠之罪也。然改事为史则其徒弑君之罪。其可尽掩乎。明宗不发丧之罪。其可尽讳乎。文克谦在毅宗之初。言人所不能言。故谓之凤鸣朝阳。乃于晚年介于凶贼之间。脂韦鸡头。难免不胜权舆之叹。然既为在实录则是可尚也。虽阴祈兢改数字。不改固可也。柰何没实而以来不妨医作玉堂人之句乎。其有愧于南蕫氏之执简以从大矣。
神宗为崔忠献之所立。不能明正忠献之罪。以力量所不及也。而明宗寝疾之日。欲遣医进药。尚有天伦之恩也。及其薨也。欲以王礼葬之。尚念继祖之重也。此虽见格于忠献而未果。比诸明宗不发毅宗之丧。受西师之声讨。犹足谓未全昏昧也。噫彼忠献以何凶肚废之也。已犯伦纲而必使用降等之礼于宾天之君。是可忍为乎。康兆,仲夫身伏天诛。而忠献之延及四世。天理诚不可知也。
韩惟汉隐于智异山。本史曰见忠献擅政曰乱将作矣。遂絜家隐山。除官不起。未几果有契丹蒙元之乱。其擅政二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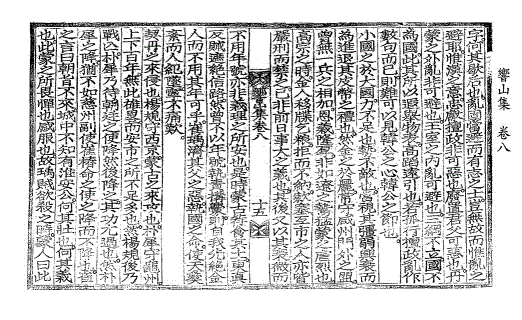 字。何其歇后也。乱固当避而有志之士。岂无故而惟乱之避耶。惟汉之意。忠献擅政非可恶也。废置君父可恶也。丹蒙之外乱非可避也。王室之内乱可避也。三纲不立。国不为国。此其所以遐举物表。高蹈远引也。若孤行擅政乱作数句而已。则难可以见韩公之心韩公之节也。
字。何其歇后也。乱固当避而有志之士。岂无故而惟乱之避耶。惟汉之意。忠献擅政非可恶也。废置君父可恶也。丹蒙之外乱非可避也。王室之内乱可避也。三纲不立。国不为国。此其所以遐举物表。高蹈远引也。若孤行擅政乱作数句而已。则难可以见韩公之心韩公之节也。小国之于大国。力不足也势不敌也。当视其彊弱兴衰而为进退其皮币之礼也。然金之于丽。常守咸州门外之盟。曾无一兵之相加。恩义隆厚。非如辽之鸷猛蒙之虐烈也。高宗之时。金人移牒乞粮。拒而不纳。款塞互市之人亦皆严刑而禁之。已非前日事大之义也。其后又以其衰微而不用年号。亦非义理之所安也。是时蒙古荐食其土。东真反贼遮绝信路。然曾不以年号执责搆衅。则自我先绝金人而不用其年可乎。崔瑀济其父之恶。执国之命。使天彝紊而人纪坠。宁不痛叹。
契丹之来侵也。杨规守西京。蒙古之来攻也。朴犀守龟州。上下百年。无此雄略。而安市之所不足多也。然杨规后乃战亡。朴犀乃待朝廷之使降然后降之。其功尤过也。然朴犀之降。犹不如慈州副使崔椿命之使之降而不降也。崔之言曰朝旨不来。城中不知有淮安公。何其壮也。何其义也。此蒙之所畏惮也感服也。故瑀贼欲杀之时。蒙人曰此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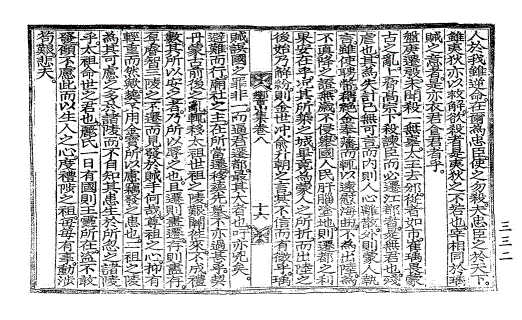 人于我虽逆命。在尔为忠臣。使之勿杀。夫忠臣之于天下。虽夷狄亦以救解。欲杀者是夷狄之不若也。宰相同于瑀贼之意者。是亦衣君食君者乎。
人于我虽逆命。在尔为忠臣。使之勿杀。夫忠臣之于天下。虽夷狄亦以救解。欲杀者是夷狄之不若也。宰相同于瑀贼之意者。是亦衣君食君者乎。盘庚迁殷。未闻杀一无辜。太王去邠。从者如市。崔瑀畏蒙古之乱。上胁高宗。下杀谏臣而必迁江都者。是无君也。残虐也。其为失计已无可言。而内则人心离散。外则蒙人执言。虽使聘币。称绝金奉藩。而辄以远慰海曲。不为出陆。为不真降之證。无岁不侵。举国人民肝脑涂地。则迁都之利果安在乎。况其所筑之城。毕竟为蒙人之所折。而出陆之后始乃解纷。则金世冲,俞升朝之言。其不信而有徵乎。瑀贼误国之罪非一。而逼君迁都。最其大者也。吁亦凶矣。
避难而行。庙社之主。在所当迁。移葬先墓。不亦过甚乎。契丹蒙古前后之乱。辄移太祖世祖之陵。艰关往来。不成礼数。其所以安之者。乃所以辱之也。且迁则尽迁。存则尽存。厚睿智三陵之不迁而见发于贼手何哉。尊祖之心。抑有轻重而然欤。葬不用金宝。所以虑窃发之患也。二祖之陵为其可虑之多于诸陵。而不自知其患生于所忽之诸陵乎。太祖命世之君也。丽氏一日有国则王灵所在。盗不敢发。顾不虑此而以生人之心。度礼陟之祖。每每有事。动涉苟艰。悲夫。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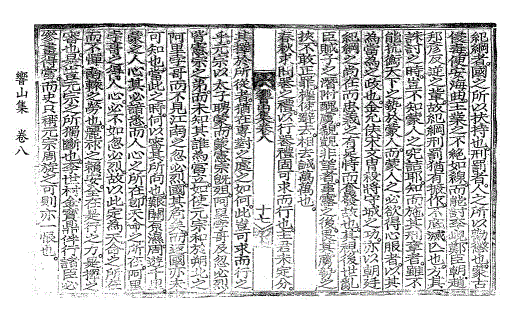 纪纲者。国之所以扶持也。刑罚者。人之所以劝惩也。蒙古侵毒。便安海曲。王业之不绝如线。而能讨李岘,郑臣朝,赵邦彦反逆之辈。故纪纲刑罚犹有振作。不底灭亡也。方其诛讨之时。岂不知蒙人之究诘耶。知而施其刑章者。虽不能抗衡天下之势于蒙人。而蒙人之必欲得心服者。以其为当为之政也。金允侯,宋文胄杀将守城之功。亦以朝廷纪纲之尚在而忠义之有足恃而奋发故也。其视后世乱臣贼子之潜附丑虏。
纪纲者。国之所以扶持也。刑罚者。人之所以劝惩也。蒙古侵毒。便安海曲。王业之不绝如线。而能讨李岘,郑臣朝,赵邦彦反逆之辈。故纪纲刑罚犹有振作。不底灭亡也。方其诛讨之时。岂不知蒙人之究诘耶。知而施其刑章者。虽不能抗衡天下之势于蒙人。而蒙人之必欲得心服者。以其为当为之政也。金允侯,宋文胄杀将守城之功。亦以朝廷纪纲之尚在而忠义之有足恃而奋发故也。其视后世乱臣贼子之潜附丑虏。春秋求问丧之礼。以行丧礼固可求而行也。主君未定分。其择于所从者。犹在专对之处之如何。此岂可求而行之乎。元宗以太子聘蒙。而蒙宪宗既殂。阿里孛哥及忽必烈皆宪宗之弟。而未知其谁为当立。如使元宗和于朔北之阿里孛哥而不见江南之忽必烈。国其危矣。而返国亦未可知也。当此之时。何以审其所向也。艰关原湿。周游千里。蒙之人心其必谙悉。而人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阿里孛哥之得人心。必不如忽必烈。故以此定为天命之所在而不惮南辕之劳也。丽祚之赖安。全在是行之力。是择之审也。是岂元宗之所独断也。李世村,金宝鼎伴行诸臣必参画得当。而史只称元宗周旋之可则亦一恨也。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3L 页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移其教不易其俗。圣人御世之本也。忽必烈能知御世之本。故立约之初二曰衣冠从本国之俗。皆不改易。其为本国之幸为何如也。所惜者忠烈忠宣入尚公主。乃效元人开剃编发之法。其得罪于元祖而忝元宗之功大矣。彼之靡风奇技之惟务。虽非连昏公主之亲。而惟胡服是尚。胡俗是慕。又非得罪于忠烈,忠宣者乎。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移其教不易其俗。圣人御世之本也。忽必烈能知御世之本。故立约之初二曰衣冠从本国之俗。皆不改易。其为本国之幸为何如也。所惜者忠烈忠宣入尚公主。乃效元人开剃编发之法。其得罪于元祖而忝元宗之功大矣。彼之靡风奇技之惟务。虽非连昏公主之亲。而惟胡服是尚。胡俗是慕。又非得罪于忠烈,忠宣者乎。书曰蓄疑败谋。君而多疑。宁得以保其邦而安其民乎。倭人其始侵扰。不过贼倭之事。一番聘好之后。其酋长还戢其贼而杀之。则其邻谊固自在也。元主以贪婪之心。欲致倭人者。自云不过欲得一统之美名。夸示于竹帛之间也。在元宗之地。虽有彼命。指陈利害。勿兴无名之师。而使吾民不受其弊。使元人不损其威可也。虑不及此。惟以目前承顺为恭。如李藏用之忠告于使臣者。反疑有二心。欲流绝岛。非惑之甚者乎。元命之可畏。甚于倭衅之可恶。然元主固英雄也。如使藏用之言得闻。是固合于帝王御戎之道也。安知不蒙其采纳乎。畏心在内。疑情在外。智士不得为谋。自元宗以及忠烈。疲于为元先驱而肝脑涂地。国家虚耗。不亦可惜乎。
甚矣元宗之柔弱也。既使林衍杀金俊则政归林衍势也。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4H 页
 于其政归之时。不思裁抑之道。卒受废处之辱。此一柔弱也。既因蒙人之力复位而如蒙。则于对辨之时。虽有衍子惟干之伺窥。而蒙力之尚有可恃。则何不直言废立之事。而乃待白文节,李藏用之言然后。始乃以实奏乎。此二柔弱也。柔弱如是。林衍之不诛。其子惟茂之袭拜。无足怪也。然所可疑者。以蒙主之威明。既知废立之由。何不令诛衍而明其顺逆之分乎。不惟不诛衍。如惟干之徒。从而留置。后与世子谌争归于征倭之时。何其倒置之甚乎。李藏用当废立之际不救止。反出逊位之言。史氏以春秋不越境之义责之宜矣。然前后辨质蒙朝。得以复位而返国。皆藏用之功也。犹可谓唐之狄仁杰也。
于其政归之时。不思裁抑之道。卒受废处之辱。此一柔弱也。既因蒙人之力复位而如蒙。则于对辨之时。虽有衍子惟干之伺窥。而蒙力之尚有可恃。则何不直言废立之事。而乃待白文节,李藏用之言然后。始乃以实奏乎。此二柔弱也。柔弱如是。林衍之不诛。其子惟茂之袭拜。无足怪也。然所可疑者。以蒙主之威明。既知废立之由。何不令诛衍而明其顺逆之分乎。不惟不诛衍。如惟干之徒。从而留置。后与世子谌争归于征倭之时。何其倒置之甚乎。李藏用当废立之际不救止。反出逊位之言。史氏以春秋不越境之义责之宜矣。然前后辨质蒙朝。得以复位而返国。皆藏用之功也。犹可谓唐之狄仁杰也。金珠之贡。侯度方物之所宜也。非其当贡而蒙人之来采者何也。本国之许采者何也。好铜之求。纳之鍮锡。谓之不实。则蒙人之廉。始有可观。终为叛逆兴利之说所动。糜弊遐土。是不宝远物之道乎。若其断地之脉。渴天之产。斲丧元气。灾孽荐臻。病入膏肓。莫能谏止。丽祚之衰。职曰于此。非可恨之甚乎。
忠烈之胡服。观于元祖约束。及后辨问之说。则非元之使变也。乃忠烈之自变也。忠烈虽欲自变。非臣人之逢迎则何能独断也。前则有印公秀。后则有姜允绍。此二人者。人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4L 页
 面夷心也。始劝元宗而不得。终陷忠烈于妙年。使礼乐文章之俗。一朝归于开剃而编发。欲以求媚于元人者。反取其诘责。为天下万世之罪人。岂非举国之羞乎。
面夷心也。始劝元宗而不得。终陷忠烈于妙年。使礼乐文章之俗。一朝归于开剃而编发。欲以求媚于元人者。反取其诘责。为天下万世之罪人。岂非举国之羞乎。卖官鬻爵。桓灵以后为国计者。宜有所戒也。鬻卖所得之货。果补国用而能延得国脉乎。私自宫市。渎乱官坊。已为丧国之本。况立定鬻官之法。以为令于一国。科等敛银以纳都监者。诚为寒心也。所谓都兵马使始作俑而不见其名。史例可疑。驰聘弋猎。峻宇雕墙之主。惟以得财为喜。宁恤国之将亡乎。
春秋子无雠母之义。忠烈废太妃王氏。流弟顺安公琮于海岛。人伦之变极矣。从古间人父母兄弟者必称咀咒。咀咒之说安有其实也。汇类历考。不难辨明。而每每堕于奸宵之术。如忠烈者胡服之人也。无足责焉。而却念胡人亦有父子之亲。以此表率。其贻羞为何如也。赵仁规可谓当时贤宰。而为其使臣。甚可惜也。苟无柳璥之一谏。朝廷无足观矣。
福善祸淫之理。谓之无可乎。谓之有可乎。夫金上洛之忠贞。忠烈时一人也。韦得儒,卢进义以私怨搆诬于忻都及洪茶丘。及其对辨元朝之时。得儒,进义得烂舌之病而死。忻都,茶丘尚不死而惟反侧是事。何理之验于得儒,进义。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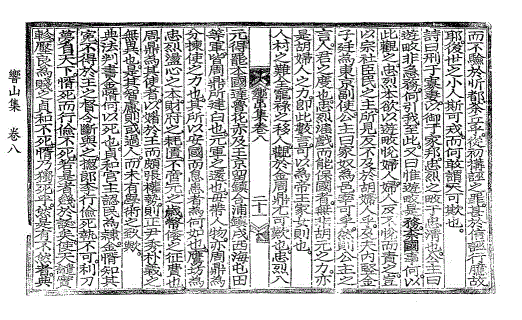 而不验于忻都,茶丘乎。从初搆诬之罪。甚于信诬行臆故耶。后世之小人斯可戒。而何敢谓天可欺也。
而不验于忻都,茶丘乎。从初搆诬之罪。甚于信诬行臆故耶。后世之小人斯可戒。而何敢谓天可欺也。诗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忠烈之畋于忠清也。公主曰游畋非急务。何引我至此。又曰惟游畋是务。柰国事何。以此观之。忠烈本欲以游畋悦妇人。妇人反不悦而责之。岂以宗社臣民之主。所见反不及于胡妇人乎。及夫内竖金子廷为东京副使。公主曰家奴为邑宰可乎。然则公主之言。人君之度也。忠烈淫戏而能保国者。无非胡元之力。亦是胡妇人之力。即此数言。可以为帝王家女则也。
人材之难全。宠禄之移人。观于金周鼎尤可叹也。忠烈入元。得罢本国达鲁花赤及王京留镇合浦镇戍西海屯田等军。皆周鼎所建白也。元军之还也。毋带人物。亦周鼎为分拣使之力也。其所以安国而息患者为何如也。鹰坊为忠烈荡心之本。财府之耗匮。不啻元之岁币倭之征费也。周鼎为其使者。以媚于王而颇张权势。则正尹秀,朴义之无异也。是其智虑则或过人。而未有学术之致欤。
典法判书金㥠何以死也。贞和宫主认民为隶。金㥠知其冤。不得于王之督令断与之。揔郎李行俭死执不可。利刀梦自天下。㥠死而行俭不死。若是者几于诞矣。使天谴实轸。压良为贱之贞和不死。㥠乃独死乎。然是有不然者。典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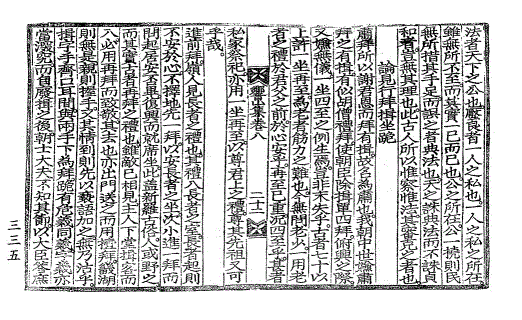 法者天下之公也。压良者一人之私也。一人之私之所在。虽无所不至。而其实一己而已也。公之所在。公一挠则民无所措其手足。而误之者典法也。天之诛典法而不诛贞和者。岂无其理也。此古人所以惟察惟法。其审克之者也。
法者天下之公也。压良者一人之私也。一人之私之所在。虽无所不至。而其实一己而已也。公之所在。公一挠则民无所措其手足。而误之者典法也。天之诛典法而不诛贞和者。岂无其理也。此古人所以惟察惟法。其审克之者也。论见行拜揖坐跪
肃拜所以谢君恩而拜有揖。故名为肃也。我朝中世嫌肃拜之有揖。有似胡僧礼拜。使朝臣除揖单四拜。俯兴之际。又嫌无仪。一坐四至之例生焉。岂非末失乎。古者七十以上许一坐再至。为老者筋力之难也。今无问老少。一用老者之礼于君父之前。于心安乎。再至已重。况四至乎。甚者私家祭祀。亦用一坐再至。以尊君上之礼。尊其先祖又可乎哉。
进前拜。岭人见长者之礼也。其礼入长者之室。长者起则不安于心。不择地先一拜。以安长者之坐。次小进一拜而问起居安否毕。复兴而就席坐。此盖新罗古俗。人或野之。而其实古者再拜之礼也。虽敌己相见。主人下堂揖客而入。必用再拜而致敬。其去也亦出门送之而用揖拜。畿湖则无是。亲则握手。又其情到则先以亵语加之。无乃沽乎。
揖字手齐口耳间。与两手下为拜。跪有危义同义。字义亦当深究。而自废揖之后。朝士大夫不知其节。以大臣答庶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6H 页
 僚时。举手上衡为揖。此非揖。即古所谓空首拜也。空首者首不至地之名。君答臣之礼也。孔子揖所与立。揖是立时容。坐答者岂为揖乎。今台谏遇大官于道。所由先请。相揖礼于录事。举皆权停。而或可行之则必于轩马上立而相揖。此古礼之尚存也。
僚时。举手上衡为揖。此非揖。即古所谓空首拜也。空首者首不至地之名。君答臣之礼也。孔子揖所与立。揖是立时容。坐答者岂为揖乎。今台谏遇大官于道。所由先请。相揖礼于录事。举皆权停。而或可行之则必于轩马上立而相揖。此古礼之尚存也。丧人稽颡礼也。与人书恒用之。而其对吊客。未见有行之者。其小谨者式块而已。否则平坐无戚容。能有三年之哀于其心乎。此非他。平时既不用再拜之礼。故居丧遂不知拜而后稽颡。稽颡而后拜之节也。又未见有下堂迎吊者。此平时不知揖让故也。
宗室顺川君家。礼见尊行。年虽少必先拜之。尊行坐答而已。有服则犹可也。施于无服。莫失于过乎。
父兄召使礼于尊客。拜后不敢同席坐。必侍立父兄之侧。京中此礼甚当。岭人鲜有行之者。
跪坐安坐跏趺坐。皆有明證。今之交股谓之平坐。未知何所据。立一膝蹠一足。今无名以拜之。屈一膝为奇拜则此亦名奇坐可也。立两膝而坐。今谓蹲坐。蹲之称本有退安之意。立膝乌在其退安乎。以俚则躁坐。躁有躁动之意。似或近之。见今儒宫文会。少者听长者之命用此坐。京中子弟侍坐父兄亦然。盖以不安席不能容为恭。此甚善。然古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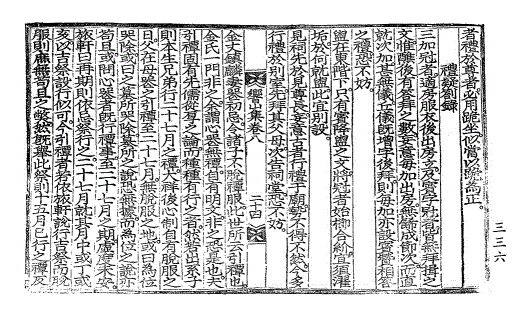 者礼于尊者。必用跪坐。似当以跪为正。
者礼于尊者。必用跪坐。似当以跪为正。礼疑劄录
三加冠者。适房服衣后出房立。及宾字冠者。皆无拜揖之文。惟醮后有答拜之数。妄意每加出房。无饰成节次。而直就次加。甚无仪。丘仪既增字后拜。则每加亦设宾赞相答之礼。恐不妨。
盥在东阶下。只有宾降盥之文。将冠者始栉合紒。宜须濯垢。于何就盥。此宜别设。
见祠先于见尊长。妄意古者行礼于庙。势不得不然。今多行礼于别室。先拜其父母。次告祠堂。恐不妨。
金丈镇麟妻丧初忌。令诸子不脱禫服。此世所云引禫也。金氏一门非之。余谓心丧无禫。自有明文。非之恐是也。夫引禫固有先儒从厚之论。而种种有行之者。然若出系子则本生兄弟行二十七月之禫。大祥后心制自有脱服之日。父在母丧之引禫至二十七月。无脱服之地。或曰为位哭除。或曰之墓所哭除。墓所之说恐无据。而为位之说亦苟且。或问心丧者既行禫事。至二十七月之期。虚度未安。旅轩曰再期则依忌祭行之。二十七月就其月中或丁或亥。以吉祭设行似可。今引禫者若依旅轩说行吉祭而脱服则庶无苟且之弊。然既举此祭则十五月已行之禫反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7H 页
 归虚文。而二十七月之祭。能无重禫之嫌乎。此吉祭似指丧毕祫享而言。然父在母丧无祫享之礼。此不敢知也。古礼严二尊之嫌而犹许心丧以至再期者。已所以引而伸之者也。似不可以加厚也。
归虚文。而二十七月之祭。能无重禫之嫌乎。此吉祭似指丧毕祫享而言。然父在母丧无祫享之礼。此不敢知也。古礼严二尊之嫌而犹许心丧以至再期者。已所以引而伸之者也。似不可以加厚也。春阳权氏一人有父在丧妻。其子有胜冠者。李成远以为父在为妻不禫。十五月不行禫。使其子祇于朔奠变制。十一月练期亦已如是。按小记为母妻禫。疏云父在适子不杖。不杖不禫。成远之言必据此也。夫父在父主祭。经无为适子妇行禫之文。故疏说亦曰父在不为妻禫也。然疏但言父在。不言子在。此或为无子妻而言也。父主妇丧。祖不压孙。则为孙者不伸十五月之禫于其母。于情礼为何如也。且为妻行禫。是报服三年之体。非为其子也。然父于长子应禫。则为长妇行禫。使孙为其母具得三年之体。恐无大害也。
真宝一士人有前妻初忌前。遭后妻丧。立嗣发丧。受服之际。甲曰当为前母追服心丧。而为后母服重。用包特之礼可也。乙曰服无始受而遽追心丧。已非礼意。且心丧之服不过表心之制。而恐不列于麻葛包特之间也。余则以乙说为是。问者曰若不为前母心制。则朝夕几筵。以后母服行之可乎。余曰几筵同设一室则以重服并行馈奠。恐无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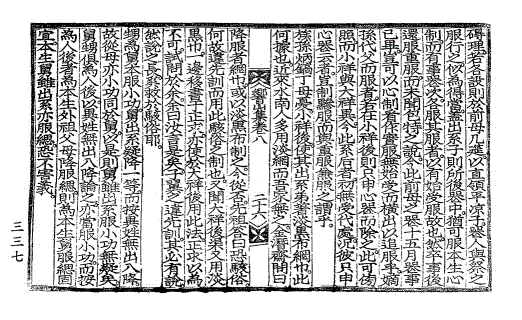 碍理。若各设则于前母几筵。以直领平凉子。丧人与祭之服行之。似为得当。盖出系子则所后丧中。犹可服本生心制。而有事丧次。各服其服者。以有始受服故也。然卒事后还服重服。而未闻包特之说。今此前母之丧十五月丧事已毕。岂可以心制看作实服。无始受而横出以追服乎。嫡孙代父而服者。若在小祥后则只申心丧而除之。此可傍照。而小祥与大祥异。今此系后者。初无受代处。况彼只申心丧云者。岂制黪服而与重服兼服之谓乎。
碍理。若各设则于前母几筵。以直领平凉子。丧人与祭之服行之。似为得当。盖出系子则所后丧中。犹可服本生心制。而有事丧次。各服其服者。以有始受服故也。然卒事后还服重服。而未闻包特之说。今此前母之丧十五月丧事已毕。岂可以心制看作实服。无始受而横出以追服乎。嫡孙代父而服者。若在小祥后则只申心丧而除之。此可傍照。而小祥与大祥异。今此系后者。初无受代处。况彼只申心丧云者。岂制黪服而与重服兼服之谓乎。族孙炳镐丁母忧。小祥后。使其出系弟著淡黑布网巾。此何据也。近来水南人多用淡网而吾家无之。金潜斋问曰降服者网巾。或以淡黑布制之。今从否。先祖答曰恐骇俗。何故违先训而用此骇俗之制也。又闻大祥后渠又用淡黑巾。一边移书于正求。亦使于大祥后用此法。正求以为不可。试问于余。余曰汝言是矣。子翼之违先训。其必有说。然说之长。奚救于骇俗耶。
甥为舅本服小功。舅出系疑降一等。而按异姓无出入降。故从母亦小功同于舅。以是则舅虽出系服小功无疑矣。舅甥俱为人后。以异姓无出入降论之。亦当服小功。而按为人后者为本生外祖父母降服缌。则为本生舅服缌固宜。本生舅虽出系亦服缌。恐不害义。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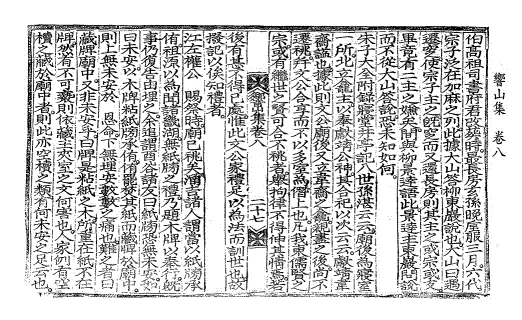 伯高祖司书府君改葬时。最长房玄孙晚垕服三月。六代宗子泛在加麻之列。此据大山答柳东岩说也。大山曰遇迁窆。使宗子主之。既窆而又还长房则其主之或宗或支。毕竟有二主之嫌矣。间与柳景达语此。景达主东岩问说而不从大山答说。恐未知如何。
伯高祖司书府君改葬时。最长房玄孙晚垕服三月。六代宗子泛在加麻之列。此据大山答柳东岩说也。大山曰遇迁窆。使宗子主之。既窆而又还长房则其主之或宗或支。毕竟有二主之嫌矣。间与柳景达语此。景达主东岩问说而不从大山答说。恐未知如何。朱子大全附录寝堂井亭记八世孙湛云云。庙后为寝室一所。北立龛主。以奉献靖公神。其合祀以次云云。献靖韦斋谥也。据此则文公庙后又立韦斋之龛。亲尽之后。尚不迁祧。并文公合享而不以多室为僭上也。凡我东儒贤之宗。或有继世之贤可合不祧者。举拘律不得伸其情焉。若后有甚不得已处。惟此文公家礼足以为法而训世也。故拨记以俟知礼者。
江左权公 赐祭时。庙已祧矣。涵吉诸人谓当以纸榜承侑。祖源以为闻诸畿湖。无纸榜之礼。乃题木牌以奉行。既事仍复告由埋之。余追谓酉谷诸友曰纸榜恐无未安。如曰未安。以木牌粘纸榜承侑。侑罢焚其纸而藏牌于庙中。则上无未安于 恩命。下无埋安数数之痛也。难之者曰藏牌庙中。又非未安乎。曰牌是粘纸之木。所重在纸不在牌。然有不可亵则依藏主夹室之文何害也。人家例有空椟之藏于庙中者。则此亦空椟之类。有何未安之足云也。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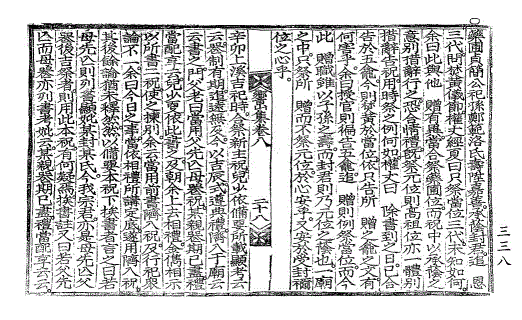 药圃贞简公祀孙郑范洛氏寿升嘉善。承荫封君。追 恩三代。问焚黄仪节。权丈经夏曰只祭当位三代。未知如何。余曰此与他 赠有异。当合祭药圃位。而祝中以承荫之意别措辞行之。恐合情礼。既祭元位则高祖位亦一体别措辞告祝。用时祭之例何如。权丈曰 除书到之日。已合告于五龛。今则焚黄于当位。依只告所 赠之龛之文。有何害乎。余曰授官则遍告五龛。追 赠则例祭当位。而今此 赠职虽以子孙之寿。而封君则乃元位之荫也。一庙之中。只祭所 赠而不祭元位。于心安乎。又安于受封祢位之心乎。
药圃贞简公祀孙郑范洛氏寿升嘉善。承荫封君。追 恩三代。问焚黄仪节。权丈经夏曰只祭当位三代。未知如何。余曰此与他 赠有异。当合祭药圃位。而祝中以承荫之意别措辞行之。恐合情礼。既祭元位则高祖位亦一体别措辞告祝。用时祭之例何如。权丈曰 除书到之日。已合告于五龛。今则焚黄于当位。依只告所 赠之龛之文。有何害乎。余曰授官则遍告五龛。追 赠则例祭当位。而今此 赠职虽以子孙之寿。而封君则乃元位之荫也。一庙之中。只祭所 赠而不祭元位。于心安乎。又安于受封祢位之心乎。辛卯上溪吉祀时。合祭新主祝。儿少依备要所载显考云云。丧制有期。追远无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礼。隮入于庙云云书之。门父老曰当用父先亡母丧祝。某亲丧期已尽。礼当配享云。儿少更依此书之。及朝余上去相礼。金俊相示以所书二祝。使之拣别。余云当用前书隮入祝。及行祀众论不一。余曰今日之事。当依相礼所讲定底。遂用隮入祝。其后馀论犹未释然。然以备要本祝下挨书者言之曰若母先亡则列书显妣某封某氏。今我宗君。亦是母先亡父丧后吉祭者。则用此本祝。有何疑焉。挨书注又曰若父先亡而母丧亦列书考妣云。某亲丧期已尽。礼当配享云云。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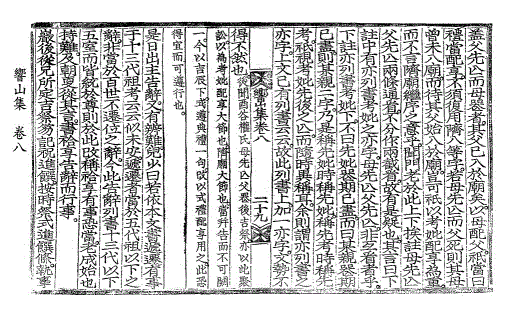 盖父先亡而母丧者。其父已入于庙矣。以母配父。祇当曰礼当配享。不须复用隮入等字。若母先亡而父死则其母曾未入庙。而待其父始入于庙。岂可祇以考妣配享为重。而不言隮庙继序之意乎。闻门老于此上下挨注母先亡父先亡两条通看。不分作两截看。故有是疑也。其言曰下注中有亦列书考妣之亦字。母先亡父先亡。非互看者乎。下注亦列书考妣下。不曰先妣丧期已尽。而曰某亲丧期已尽。则某亲二字。乃是称先妣时称先妣。称先考时称先考。祇视考妣先后之亡。而随时异称耳。余则谓亦列书之亦字。上文已有列书云云。故此列书上。加一亦字。文势不得不然也。(后闻酉谷权氏母先亡父丧后吉祭。亦以此聚讼。以为考妣配享大节也。隮庙大节也。当并告而不可阙一。今以吉辰下。式遵典礼一句。改以式礼配享用之。此恐得宜而可遵行也。)
盖父先亡而母丧者。其父已入于庙矣。以母配父。祇当曰礼当配享。不须复用隮入等字。若母先亡而父死则其母曾未入庙。而待其父始入于庙。岂可祇以考妣配享为重。而不言隮庙继序之意乎。闻门老于此上下挨注母先亡父先亡两条通看。不分作两截看。故有是疑也。其言曰下注中有亦列书考妣之亦字。母先亡父先亡。非互看者乎。下注亦列书考妣下。不曰先妣丧期已尽。而曰某亲丧期已尽。则某亲二字。乃是称先妣时称先妣。称先考时称先考。祇视考妣先后之亡。而随时异称耳。余则谓亦列书之亦字。上文已有列书云云。故此列书上。加一亦字。文势不得不然也。(后闻酉谷权氏母先亡父丧后吉祭。亦以此聚讼。以为考妣配享大节也。隮庙大节也。当并告而不可阙一。今以吉辰下。式遵典礼一句。改以式礼配享用之。此恐得宜而可遵行也。)是日出主告辞。又有辨难。儿少曰若依本文书递迁有事于十三代祖考云云似未安。递迁者当于五代祖以下之辞。非当于百世不迁位之辞。今此告辞列书十三代以下五室而皆统于尊则于此改称祫享有事恐当。老成始也持难。及朝更从其言。书祫享告辞而行事。
岩后从兄所定吉祭笏记祝进馔。按时祭式进馔条。执事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39L 页
 者一人奉鱼肉。一人奉米面食。一人奉羹饭云云。此祝字代以执事者恐好。虞祔则进馔上有祝字。吉祭恐与虞祔不同耳。又笏记中利成之利字改作礼字。分注云御讳改礼。按利字虽音同成平声。御讳上声。音之高低不同。直用本文恐无未安。
者一人奉鱼肉。一人奉米面食。一人奉羹饭云云。此祝字代以执事者恐好。虞祔则进馔上有祝字。吉祭恐与虞祔不同耳。又笏记中利成之利字改作礼字。分注云御讳改礼。按利字虽音同成平声。御讳上声。音之高低不同。直用本文恐无未安。祝立西阶上东向告利成。降复位。与在位者皆再拜。金稚长曰在位者。指诸执事之与祝同佐主人于庙中者。非尊长凡员之在列与祭者。盖利成拜。所以庆主人之受嘏而拜于神前也。此意似好。抑有可据耶。参神曰主人以下再拜。辞神曰主人以下皆再拜。独于利成拜曰与在位者皆再拜。为其称举之有别而有此分属之异耶。利成时主人既不拜。则不可称主人以下。而曰在位者。理所必然也。在位之称。何独归之诸执事。而谓尊长及凡员不在其中也。徐当更详。
妙枝洞墓祀笏记及祝式。中世三年一祭时所讲定而行之者也。然笏记中先降后参之节则吾王考釐为先参后降。手墨尚新。祝文之改为见行之式者。岩后兄所定。而笏祝中又有可商者。敢逐节僭书于左。
笏记终献后无侑食一段。考家礼本文果然矣。然先祖答禹秋渊书曰墓祭无进馔侑食之节。或以为不设饭羹。恐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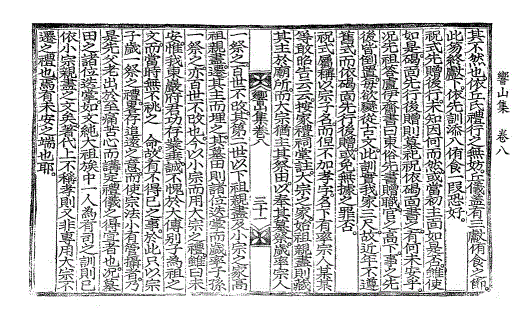 其不然也。依丘氏礼行之无妨。丘仪盖有三献侑食之节。此笏终献下。依先训添入侑食一段恐好。
其不然也。依丘氏礼行之无妨。丘仪盖有三献侑食之节。此笏终献下。依先训添入侑食一段恐好。祝式先赠后行。未知因何而然。或当初主面如是否。虽使如是。碣面先行后赠则墓祀祝依碣面书之。有何未安乎。况先祖答卢伊斋书曰东俗先书赠职。官之高下。事之先后皆倒置。每欲变从古文。此训实我家三尺。故近年不遵旧式而依碣面先行后赠。或免无据之罪否。
祝式属称以宗子名。而但不加孝字。名下有率宗人某某等敢昭告云云。按家礼祠堂注。大宗之家。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庙所。而大宗犹主其祭田。以奉其墓祭。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亲尽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迁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则诸位迭掌而岁率子孙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今以小宗而用大宗之礼。虽曰未安。惟我东岩府君功存业垂。诚不愧于大传别子为祖之文。而当时无不祧之 命。故有不得已之事。于此只以宗子岁一祭之礼。略存追远之意。而使宗法小有管摄者。乃是先父老出于至痛苦心而讲定礼仪之得宜者也。况墓田之诸位迭掌。如文纯大祖族中一人为有司之训则已依小宗亲尽之文矣。著代上不称孝则又非专用大宗不迁之礼也。焉有未安之端也耶。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0L 页
 玉山立碣时笏记。仓卒立书。而祝赞者谒者赞引及诸执事。先再拜后再拜。参用 时王庙宫之制。或无僭汰否。大抵祝赞谒。祭祀耳目之任。泛与在位者偕拜。滚同无别则行事自多窒碍矣。执事者先设蔬果。而主人后入为参降。则先设蔬果者。岂容不拜乎。赞者读笏。谒者引主人。而若不先行拜礼。则以未行拜之身。何以读笏。何以出引主人乎。此理甚较。而轻自臆定。尚有未安于心。未知知礼者以为如何。
玉山立碣时笏记。仓卒立书。而祝赞者谒者赞引及诸执事。先再拜后再拜。参用 时王庙宫之制。或无僭汰否。大抵祝赞谒。祭祀耳目之任。泛与在位者偕拜。滚同无别则行事自多窒碍矣。执事者先设蔬果。而主人后入为参降。则先设蔬果者。岂容不拜乎。赞者读笏。谒者引主人。而若不先行拜礼。则以未行拜之身。何以读笏。何以出引主人乎。此理甚较。而轻自臆定。尚有未安于心。未知知礼者以为如何。乡有一家为同枢者。未及追 赠而殁。小祥前 赠帖始到。即为改题焚黄。既改题则其属称当以丧人名。而三年之内。为子者著代于其祖先。于心为何如也。念昔吾宗叔古溪公未及焚黄而下世。待丧毕后吉祭。合行焚黄。依此行之恐当。
东国文献录从游私淑辨
高灵金友凤熙来访柏户。其袖中适有东国文献录第二册。此书不知出于何人之手。而以卷中人物之见载者推之。必是不过百年以下人所为也。因略披阅。有大可骇者。徐花潭从游。列吾先祖文纯公及曹南冥先生。又吾先祖门人题注。有以吾祖为花潭私淑。噫从游者。志同道合而往来答问之谓也。私淑者。未及亲见而师其道善其身之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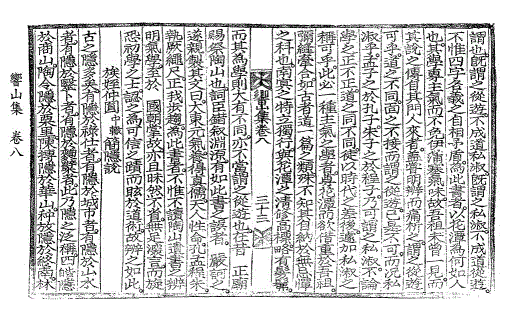 谓也。既谓之从游。不成道私淑。既谓之私淑。不成道从游。不惟四字名义之自相矛盾。为此书者。以花潭为何如人也。其学专主气而不免伊蒲塞气味。故吾祖未曾一见。而其说之传自其门人来者。盖尝明辨而痛析之。谓之从游可乎。道之不同。面之不接而谓之从游。已是不可。而况私淑乎。孟子之于孔子。朱子之于程子。乃可谓之私淑。不论学之正不正。道之同不同。徒以时代之差后。遽加私淑之称可乎。此必一种主气之学者。尊花潭而欲借重于吾祖。弥缝牵合。如古者道一篇之类。殊不知其自纳于无忌惮之科也。南冥之特立独行。与花潭之清修高标。略有髣髴。而其为学则大有不同。亦不当谓之从游也。在昔 正庙赐祭陶山也。词臣错叙渊源。有如此书之误者。 严诃之。遂亲制其文曰。大东元气。养得真儒。天人性命。孔孟程朱。执厥绳尺。正我步趋。为此书者。不惟不读陶山遗书之辨明气学。至于 国朝掌故。亦且昧然不省。无足深言。而旋恐初学之士。认之为可信之迹而眩于道术。故辨之如此。
谓也。既谓之从游。不成道私淑。既谓之私淑。不成道从游。不惟四字名义之自相矛盾。为此书者。以花潭为何如人也。其学专主气而不免伊蒲塞气味。故吾祖未曾一见。而其说之传自其门人来者。盖尝明辨而痛析之。谓之从游可乎。道之不同。面之不接而谓之从游。已是不可。而况私淑乎。孟子之于孔子。朱子之于程子。乃可谓之私淑。不论学之正不正。道之同不同。徒以时代之差后。遽加私淑之称可乎。此必一种主气之学者。尊花潭而欲借重于吾祖。弥缝牵合。如古者道一篇之类。殊不知其自纳于无忌惮之科也。南冥之特立独行。与花潭之清修高标。略有髣髴。而其为学则大有不同。亦不当谓之从游也。在昔 正庙赐祭陶山也。词臣错叙渊源。有如此书之误者。 严诃之。遂亲制其文曰。大东元气。养得真儒。天人性命。孔孟程朱。执厥绳尺。正我步趋。为此书者。不惟不读陶山遗书之辨明气学。至于 国朝掌故。亦且昧然不省。无足深言。而旋恐初学之士。认之为可信之迹而眩于道术。故辨之如此。族侄仲圆(中辙)简隐说
古之隐多矣。有隐于禄仕者。有隐于城市者。有隐于山水者。有隐于医卜者。有隐于曲蘖者。此乃隐之泛称。四皓隐于商山。陶令隐于栗里。陈抟隐于华山。种放隐于终南。林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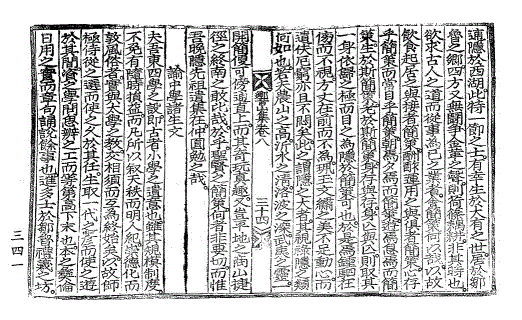 逋隐于西湖。此特一节之士。有幸生于大有之世。居于邹鲁之乡。四方又无斗争金革之声。则荷筱耦耕。非其时也。欲求古人之道而从事为己之业者。舍简策何以哉。以故饮食起居之与接者简策。酬酢运用之与俱者简策。心存乎简策而常目乎简策。朝焉夕焉而简策。游焉息焉而简策。生于斯简策。老于斯简策。身存与存。身亡与亡。则取其一身依归之极而目之为隐于简策可也。于是焉钟驷在傍而不视。方丈在前而不为。佩玉文绣之美不足动心。而遗夫(遗佚)厄穷亦且不闷矣。此之谓隐之大者。其视禄隐之类何如也。若夫农山之高。沂水之清。洛波之深。武夷之灵。一开简便可傍通直上。而其奇玩真趣。又岂平地之商山捷径之终南之敢比哉。于乎。圣贤之简策。何者非要切。而惟吾晚隐先祖遗集在。仲圆勉之哉。
逋隐于西湖。此特一节之士。有幸生于大有之世。居于邹鲁之乡。四方又无斗争金革之声。则荷筱耦耕。非其时也。欲求古人之道而从事为己之业者。舍简策何以哉。以故饮食起居之与接者简策。酬酢运用之与俱者简策。心存乎简策而常目乎简策。朝焉夕焉而简策。游焉息焉而简策。生于斯简策。老于斯简策。身存与存。身亡与亡。则取其一身依归之极而目之为隐于简策可也。于是焉钟驷在傍而不视。方丈在前而不为。佩玉文绣之美不足动心。而遗夫(遗佚)厄穷亦且不闷矣。此之谓隐之大者。其视禄隐之类何如也。若夫农山之高。沂水之清。洛波之深。武夷之灵。一开简便可傍通直上。而其奇玩真趣。又岂平地之商山捷径之终南之敢比哉。于乎。圣贤之简策。何者非要切。而惟吾晚隐先祖遗集在。仲圆勉之哉。谕中学诸生文
夫吾东四学之设。即古者小学之遗意也。虽其规模制度。不免有随时损益。而凡所以叙天秩而明人纪。崇德化而敦风俗者。实与太学之教。交相须而互为终始矣。以故师极侍从之选而使之久于其任。生取一代之彦而使之游于其间。资之学问思辨之工而等第高下末也。本之彝伦日用之实而章句诵说馀事也。进多士于邹鲁礼义之坊。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2H 页
 范一世于尧舜熙雍之域。何其盛也。晚焘以菲材散品。重叨是席。前后凡五年于玆矣。然未得与诸生一行揖让进退之事于是学。名为教授。不知学宫之所在。称以师生。不如路人之相视。是不惟时势之使然而末流之难回也。实缘为师者鲜得其人。而如吾卤疏。往往间厕。则其平日家居。无躬行实得之工。轻出仕路。有浮华侈靡之习。己未有立。未可以立人。责己不明。未可以责人。虽欲好为人师而肆然谈道德。其于人不信从何哉。所不可废者。惟有学制一事。可见古昔之良规也。不意数年来任事者。厌其纷竞移之泮学。夫纷竞于学中者。独不纷竞于泮试乎。设官分职。各有攸司。县升州兴。次第莫严。岂可因一时之敝习而更 国家之古法耶。至于故事誊录之迹。规令禁防之书。无一见存。则只见数仞宫墙巍然于重修改观之后。而其中犹夫空空然矣。然则瘝官溺职。孰有甚于教授。而虽学中诸生。又乌得无过哉。居 国家之学而食 君上之禄。衣儒者之服而读圣贤之书。有为则尧何舜何未为僭也。自期则志伊学颜不为过也。岂可让与人一等事业而自处于卑下之地乎。况明经之业。创于汉而盛于唐宋。我东之名儒达士。亦莫不由此进身。则其选其业。固不重且严欤。其在近年。诵说之明资禀之美。亦不无贤于人者。而乃
范一世于尧舜熙雍之域。何其盛也。晚焘以菲材散品。重叨是席。前后凡五年于玆矣。然未得与诸生一行揖让进退之事于是学。名为教授。不知学宫之所在。称以师生。不如路人之相视。是不惟时势之使然而末流之难回也。实缘为师者鲜得其人。而如吾卤疏。往往间厕。则其平日家居。无躬行实得之工。轻出仕路。有浮华侈靡之习。己未有立。未可以立人。责己不明。未可以责人。虽欲好为人师而肆然谈道德。其于人不信从何哉。所不可废者。惟有学制一事。可见古昔之良规也。不意数年来任事者。厌其纷竞移之泮学。夫纷竞于学中者。独不纷竞于泮试乎。设官分职。各有攸司。县升州兴。次第莫严。岂可因一时之敝习而更 国家之古法耶。至于故事誊录之迹。规令禁防之书。无一见存。则只见数仞宫墙巍然于重修改观之后。而其中犹夫空空然矣。然则瘝官溺职。孰有甚于教授。而虽学中诸生。又乌得无过哉。居 国家之学而食 君上之禄。衣儒者之服而读圣贤之书。有为则尧何舜何未为僭也。自期则志伊学颜不为过也。岂可让与人一等事业而自处于卑下之地乎。况明经之业。创于汉而盛于唐宋。我东之名儒达士。亦莫不由此进身。则其选其业。固不重且严欤。其在近年。诵说之明资禀之美。亦不无贤于人者。而乃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2L 页
 反轻易侮忽。判为殊涂。荣枯贵贱。未免舛施。岂典谟尊阁。不足为治。而布在方册。反为虚具欤。然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或有不究义理。专务音释。不知践履。惟事口耳。则圣经贤传。徒为捷径之资。而鄙悖之事纷竞之弊。无所不至。岂非可叹之甚者乎。本学在国都中。人物之繁华。利欲之诱夺。与他有异。而窃闻近日斋中有以博奕为贤者。又有恣行淫荡。情迹莫掩者云。夫博奕似或出于落拓慷慨之馀而犹且不可。况淫荡之事。岂士类所可为乎。学令所在。不可无警。而但往来游言。有难尽信。且使此辈苟得有闻于明伦善俗之地。而道义以磨砻之。礼教以矫揉之。有以感发其心志。薰陶其德性者。安有是过而得是诮耶。然则为教授者。方自引之不暇。何可独厚望于诸生哉。嗟夫师生之礼虽废。圣师之言自在。课试之法虽弛。群居之乐犹存。苟能潜心于圣师之言。如吾今日之亲切耳闻。如遇难会处。仍与同志思而得之。辨而明之。宜无不可穷之理不可格之事。于是焉反诸心而加收敛惕励之工。制于外而无邪僻怠慢之行。积之之多。养之之久。不觉其手舞足蹈而入于昭旷之境矣。异物之迁夺。复不足为患。而吾心之中。又自有严师矣。何待强置无状之人于函席之上然后。可以修职分之所当为而副乐
反轻易侮忽。判为殊涂。荣枯贵贱。未免舛施。岂典谟尊阁。不足为治。而布在方册。反为虚具欤。然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或有不究义理。专务音释。不知践履。惟事口耳。则圣经贤传。徒为捷径之资。而鄙悖之事纷竞之弊。无所不至。岂非可叹之甚者乎。本学在国都中。人物之繁华。利欲之诱夺。与他有异。而窃闻近日斋中有以博奕为贤者。又有恣行淫荡。情迹莫掩者云。夫博奕似或出于落拓慷慨之馀而犹且不可。况淫荡之事。岂士类所可为乎。学令所在。不可无警。而但往来游言。有难尽信。且使此辈苟得有闻于明伦善俗之地。而道义以磨砻之。礼教以矫揉之。有以感发其心志。薰陶其德性者。安有是过而得是诮耶。然则为教授者。方自引之不暇。何可独厚望于诸生哉。嗟夫师生之礼虽废。圣师之言自在。课试之法虽弛。群居之乐犹存。苟能潜心于圣师之言。如吾今日之亲切耳闻。如遇难会处。仍与同志思而得之。辨而明之。宜无不可穷之理不可格之事。于是焉反诸心而加收敛惕励之工。制于外而无邪僻怠慢之行。积之之多。养之之久。不觉其手舞足蹈而入于昭旷之境矣。异物之迁夺。复不足为患。而吾心之中。又自有严师矣。何待强置无状之人于函席之上然后。可以修职分之所当为而副乐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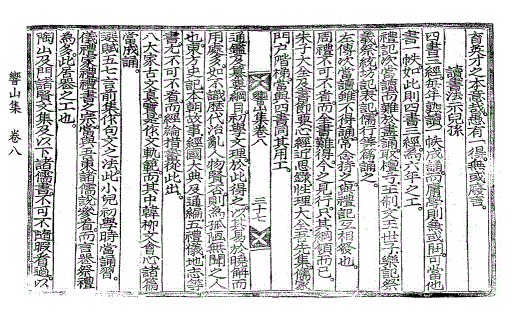 育英才之本意哉。愚有一得。无或废言。
育英才之本意哉。愚有一得。无或废言。读书法示儿孙
四书三经。每年熟读一帙成诵。而庸学则兼或问。可当他书一帙。如此则四书三经。为六年之工。
礼记次当读而难于尽诵。取檀弓,王制,文王世子,乐记,祭义,祭统,坊记,表记,儒行等篇诵之。
左传次当读。虽不得诵。常念持之。与礼记互相发也。
周礼不可不看。而全书难得。今之见行。只其纲领而已。
朱子大全及书节要心经,近思录,性理大全,吾先集。儒家门户阶梯。当与四书同其用工。
通鉴及纂要纲目。初学文理。于此得之。以其易于晓解而用处多。如不识历代治乱人物贤否。则为孤陋无闻之人也。东方史记,本朝故事,经国大典及通编,五礼仪,地志等书。尤不可不看。而经纶措画从此出。
八大家古文真宝。是作文轨范。而其中韩柳文会心诸篇当成诵。
选赋五七言前集。作句文之法。此小儿初学时当诵习。
仪礼家礼。礼书之宗。当与吾东诸儒说参看。而言丧祭礼为多。此居丧之工也。
陶山及门诸贤文集及以下诸儒书。不可不随暇看过。以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3L 页
 广见闻。
广见闻。凡读书之法。先儒之训自在。而书须是诵。读而不诵。不为己有也。为己有则理明心得。终身用之不尽矣。凡诵经传正文外。常看注说。其旨义未通者。必问质于先进。通晓乃已。他书亦用此法。则文理艰棘处。亦当自透也。然后于文章家。究作文体制。立论机轴。而会之于心。自有觉达之道也。然读书岂要作文而已哉。若乃治心修身之方。事君临民之道。以上诸书在。吾不必言。
赠权赞粹(相翊○庚戌九月四日)
谨密固好。少弘毅之象。退逊固美。少勇往奋拔之意。凡于义理文字上。一向守此门法。恐无以立主本而措诸事。日用间宜猛省也。仆不过依本分将毙人。初无见得。而只救君之偏如此云。
赠恕卿(忠镐),致俊(彦求)两宗君。
恕卿之周遍。致俊之谨慎。皆可为一门之表。而维持巩固之责。尤重于他人。每事须相议于宗中。取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跻一门于和平之域。而令后进无失家传之学。千万是企是企。庚戌八月十九日。族从晚焘书于青丘病室。
书寄三从曾孙源一(庚戌八月十八日)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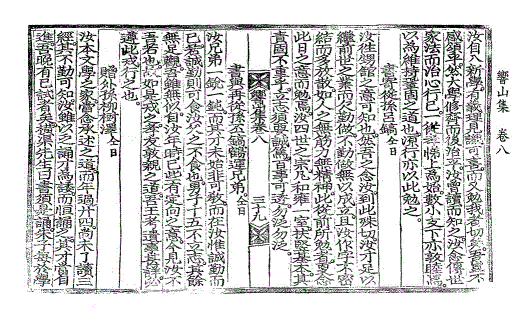 汝自入新学。有义理见识可喜。而又勉我者切矣。吾岂不感颂乎。然大学修齐而后治平。汝曾读而知之。汝念传世家法而治心行己。一从孝悌上为始。数小支下亦敦睦焉。以为维持巩固之道也。源行亦以此勉之。
汝自入新学。有义理见识可喜。而又勉我者切矣。吾岂不感颂乎。然大学修齐而后治平。汝曾读而知之。汝念传世家法而治心行己。一从孝悌上为始。数小支下亦敦睦焉。以为维持巩固之道也。源行亦以此勉之。书寄从孙吕镐(庚戌八月十八日)
汝往甥馆之意可知也。然吾之念汝。到此殊切。汝才足以继前世之业而欠勤做。不勤做无以成立。且汝作字不密结而多放散。如人之无筋力无精神。此从前所勉者。更念此日之意而勉焉。汝四世之宗。凡和雍一室。扶竖基本。其责固不重乎。立志须要诚笃。百事可透。勿泛勿泛。
书与再从孙丕镐,鹤运兄弟。(庚戌八月十八日)
汝兄弟一锐一钝。而其才未始非可教。而在汝惟诚勤而已。若诚勤则可食汝父之不食也。男子十五不立志。其馀无足观。吾虽无似。自汝年时已些有定向之意。今见汝不吾若也。故如是戒之。孝友敦亲之道。吾王考遗事甚详。必遵此戒行之也。
赠外孙柳树泽(庚戌八月十八日)
汝本文学之家。当念承述之道。而年过廿四。尚未了读三经。其不勤可知。汝虽以乏诵才为诿。而恒诵之。其才当自进。吾晚有已试者矣。横渠先生曰书须是诵。朱子每于学
响山文集卷之八 第 344L 页
 者。以是勉之。盖以不诵。不为己物故也。然己物云者。岂誊口舌而已乎。知行二者。如车轮鸟翼焉。吾固能言而已。归究汝家先集。念念孜孜。
者。以是勉之。盖以不诵。不为己物故也。然己物云者。岂誊口舌而已乎。知行二者。如车轮鸟翼焉。吾固能言而已。归究汝家先集。念念孜孜。寄示曾孙鹤旭(庚戌八月十八日)
吾病伏穷山。汝生四岁。尚不见面矣。闻已能言。次当学数与方名而入学矣。须从汝祖训戒。勿惰勤做。以张我传世之业。为善人君子。是吾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