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x 页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记
记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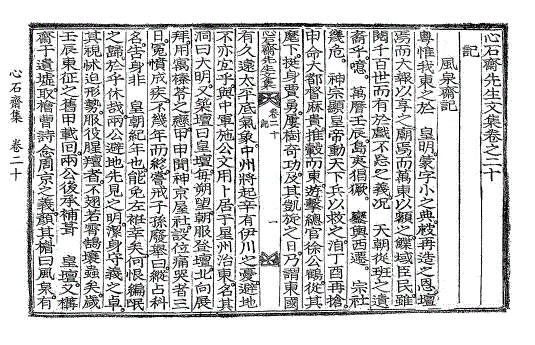 风泉斋记
风泉斋记粤惟我东之于 皇明。蒙字小之典。被再造之恩。坛焉而大报以享之。庙焉而万东以额之。鲽域臣民。虽阅千百世而有于戏不忘之义。况 天朝从班之遗裔乎。噫。 万历壬辰。岛夷猖獗。 銮舆西迁。 宗社几危。 神宗显皇帝动天下兵以救之。洎丁酉再抢。申命大都督麻贵。推毂而东。游击总官徐公鹤。从其麾下。挺身贾勇。屡树奇功。及其凯旋之日。乃谓东国有久远太平底气象。中州将起辛有伊川之忧。避地不亦宜乎。与中军施公文用卜居于星州治东。名其洞曰大明。又筑坛曰皇坛。每朔望。朝服登坛。北向展拜。用寓榛苓之恋。甲申闻神京屋社。设位痛哭者三日。冤愤成疾。不几年而终。尝戒子孙废举曰。纵占科名。告身非 皇朝纪年也。能免左衽幸矣。何恨编氓之归。于乎休哉。两公避地先见之明。洁身守义之卓。其视怵迫形势。服役腥膻者。不翅若霄鹄壤虫矣。岁壬辰东征之旧甲载回。两公后承补葺 皇坛。又构斋于遗墟。取桧曹诗念周京之义。颜其楣曰风泉。有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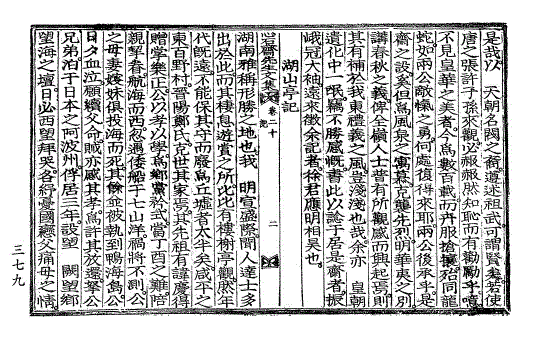 是哉。以 天朝名阀之裔。遵述祖武。可谓贤矣。若使唐之张许子孙来观。必赧赧然知耻而有劝励乎。噫。不见皇华之美者。今为数百载。而卉服抢攘。殆同龙蛇。如两公敌忾之勇。何处复得来耶。两公后承乎。是斋之设。奚但为风泉之寓慕。克袭先烈。明华夷之别。讲春秋之义。俾全岭人士普有所观感而兴起焉。则其有补于我东礼义之风。岂浅浅也哉。余亦 皇朝遗化中一氓。窃不胜感慨。书此以谂于居是斋者。振峨冠大袖。远来徵余记者。徐君应明相昊也。
是哉。以 天朝名阀之裔。遵述祖武。可谓贤矣。若使唐之张许子孙来观。必赧赧然知耻而有劝励乎。噫。不见皇华之美者。今为数百载。而卉服抢攘。殆同龙蛇。如两公敌忾之勇。何处复得来耶。两公后承乎。是斋之设。奚但为风泉之寓慕。克袭先烈。明华夷之别。讲春秋之义。俾全岭人士普有所观感而兴起焉。则其有补于我东礼义之风。岂浅浅也哉。余亦 皇朝遗化中一氓。窃不胜感慨。书此以谂于居是斋者。振峨冠大袖。远来徵余记者。徐君应明相昊也。湖山亭记
湖南雅称形胜之地也。我 明宣盛际。闻人达士多出于此。而其栖息游赏之所。比比有楼榭亭观。然年代既远。不能保其守而废为丘墟者太半矣。咸平之东百野村。晋阳郑氏。克世其家焉。其先祖有讳庆得赠掌乐正。公以孝以学。为乡党矜式。当丁酉之难。陪亲挈眷。航海而西。忽遇倭船于七山洋。祸将不测。公之母妻嫂妹俱投海而死。其馀并被执到鸭海岛。公日夕血泣。愿续父命。贼亦感其孝。为许其放还。拿公兄弟。泊于日本之阿波州。俘居三年。设望 阙望乡望海之坛。日必西望拜哭。各纾忧国恋父痛母之情。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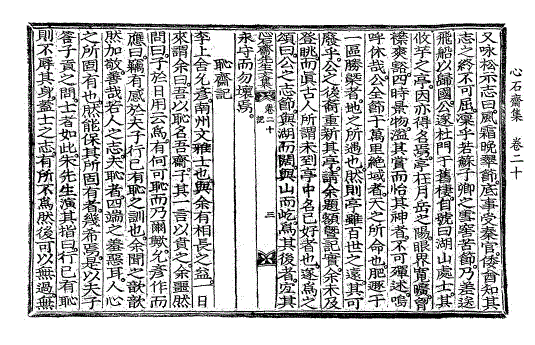 又咏松示志曰。风霜晚翠节。底事受秦官。倭酋知其志之终不可屈。凛乎若苏子卿之雪窖苦节。乃差送飞船以归国。公遂杜门于旧栖。自号曰湖山处士。其攸芋之亭。因亦得名焉。亭在月岳之阳。眼界宽旷。胸襟爽豁。四时景物。溢其赏而怡其神者。不可殚述。呜呼休哉。公全节于万里绝域者。天之所命也。肥遁于一区胜槩者。地之所遇也。然则亭虽百世之远。其可废乎。公之后裔重新其亭。请余题额暨记实。余未及登眺。而真古人所谓未到亭中名已好者也。遂为之颂曰。公之志节。与湖而阔。与山而屹。为其后者。宜其永守而勿坏焉。
又咏松示志曰。风霜晚翠节。底事受秦官。倭酋知其志之终不可屈。凛乎若苏子卿之雪窖苦节。乃差送飞船以归国。公遂杜门于旧栖。自号曰湖山处士。其攸芋之亭。因亦得名焉。亭在月岳之阳。眼界宽旷。胸襟爽豁。四时景物。溢其赏而怡其神者。不可殚述。呜呼休哉。公全节于万里绝域者。天之所命也。肥遁于一区胜槩者。地之所遇也。然则亭虽百世之远。其可废乎。公之后裔重新其亭。请余题额暨记实。余未及登眺。而真古人所谓未到亭中名已好者也。遂为之颂曰。公之志节。与湖而阔。与山而屹。为其后者。宜其永守而勿坏焉。耻斋记
李上舍允彦。南州文雅士也。与余有相长之益。一日来谓余曰。吾以耻名吾斋。子其一言以贲之。余噩然问曰。子于日用云为。有何可耻而乃尔欤。允彦作而应曰。窃有感于夫子行己有耻之训也。余闻之歆歆然加敬。善哉若人之志。夫耻者。四端之羞恶耳。人心之所固有也。然能保其所固有者。几希焉。是以夫子答子贡之问。士者如此。朱先生演其指曰。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盖士之志。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无过。无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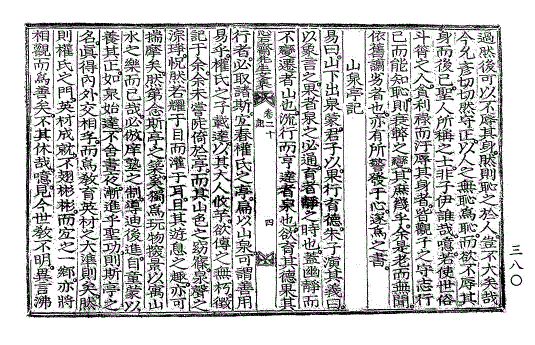 过然后可以不辱其身。然则耻之于人。岂不大矣哉。今允彦切切然守正。以人之无耻为耻。而欲不辱其身而后已。圣人所称之士。非子伊谁哉。噫。若使世俗斗筲之人。贪利禄而污辱其身者。皆观子之守志行己而能知耻。则衰弊之变。其庶几乎。余是老而无闻。依旧谫劣者也。亦有所警发于心。遂为之书。
过然后可以不辱其身。然则耻之于人。岂不大矣哉。今允彦切切然守正。以人之无耻为耻。而欲不辱其身而后已。圣人所称之士。非子伊谁哉。噫。若使世俗斗筲之人。贪利禄而污辱其身者。皆观子之守志行己而能知耻。则衰弊之变。其庶几乎。余是老而无闻。依旧谫劣者也。亦有所警发于心。遂为之书。山泉亭记
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朱子演其义曰。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静之时也。盖幽静而不变迁者山也。流行而亨达者泉也。欲育其德果其行者。必取诸斯。宜春权氏之亭。扁以山泉。可谓善用易乎。权氏之子载达。以其大人攸芋。欲传之无朽。徵记于余。余未尝陡倚于亭。而其山色之窈窱。泉声之淙琤。恍然若耀于目而灌于耳。且其游息之趣。亦可揣摩矣。然第念斯亭之筑。奚独为玩物探景以寓山水之乐而已哉。必仿庠塾之制。导迪后进。自童蒙以养其正。如泉始达。不舍昼夜。渐进乎圣功。则斯亭之名。真得内外交相孚。而为教育英材之大准则矣。然则权氏之门。英材成就。不翅彬彬。而宜之一乡。亦将相观而为善矣。不其休哉。噫。见今世教不明。异言沸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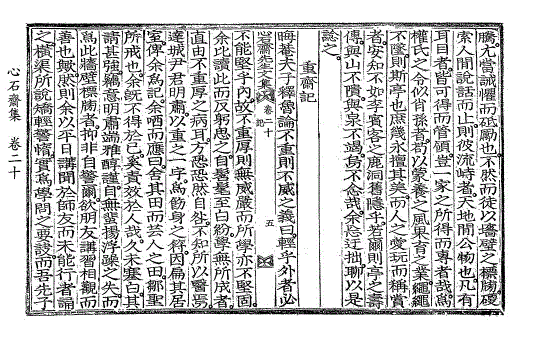 腾。尤当诫惧而砥励也。不然而徒以墙壁之标榜。硬索人閒说话而止。则彼流峙者。天地閒公物也。凡有耳目者。皆可得而管领。岂一家之所得而专者哉。为权氏之令似肖孙者。苟以蒙养之风果育之业。绳绳不坠。则斯亭也庶几永擅其美。而人之爱玩而称赏者。安知不如李宾客之鹿洞旧隐乎。若尔则亭之寿传。与山不隤。与泉不竭。乌不念哉。余忘迂拙。聊以是谂之。
腾。尤当诫惧而砥励也。不然而徒以墙壁之标榜。硬索人閒说话而止。则彼流峙者。天地閒公物也。凡有耳目者。皆可得而管领。岂一家之所得而专者哉。为权氏之令似肖孙者。苟以蒙养之风果育之业。绳绳不坠。则斯亭也庶几永擅其美。而人之爱玩而称赏者。安知不如李宾客之鹿洞旧隐乎。若尔则亭之寿传。与山不隤。与泉不竭。乌不念哉。余忘迂拙。聊以是谂之。重斋记
晦庵夫子释鲁论不重则不威之义曰。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重厚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余比读此而反躬思之。自髫髦至白纷。学无所成者。直由不重厚之病耳。方恐恐然自咎。不知所以医焉。达城尹君明肃。以重之一字。为饬身之符。因扁其居室。俾余为记。余哂而应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邹圣所戒也。余既不得于己。奚责效于人哉。久未塞白。其请甚强。窃意明肃端雅醇谨。自无蜚扬浮躁之失。而为此墙壁标榜者。抑非自警尔。欲朋友讲习相观而善也欤。然则余以平日讲闻于师友而未能行者诵之。横渠所说矫轻警惰。实为学问之要诀。而吾先子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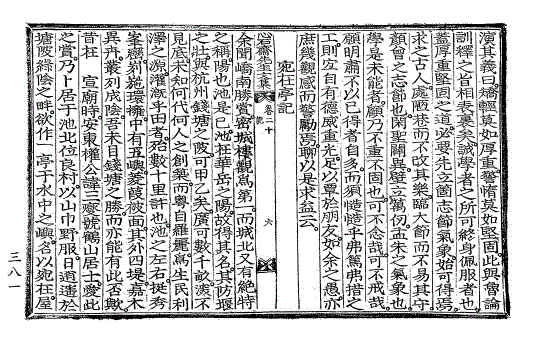 演其义曰。矫轻莫如厚重。警惰莫如坚固。此与鲁论训释之旨相表里矣。诚学者之所可终身佩服者也。盖厚重坚固之道。必要先立个志节气象。始可得焉。求之古人。处陋巷而不改其乐。临大节而不易其守。颜曾之志节也。闲圣辟异。壁立万仞。孟朱之气象也。学是未能者。顾乃不重不固也。可不念哉。可不戒哉。愿明肃不以已得者自多。而须慥慥乎弗笃弗措之工。则宜自有德威重光。足以覃于朋友。如余之愚。亦庶几观感而警励焉。聊以是求益云。
演其义曰。矫轻莫如厚重。警惰莫如坚固。此与鲁论训释之旨相表里矣。诚学者之所可终身佩服者也。盖厚重坚固之道。必要先立个志节气象。始可得焉。求之古人。处陋巷而不改其乐。临大节而不易其守。颜曾之志节也。闲圣辟异。壁立万仞。孟朱之气象也。学是未能者。顾乃不重不固也。可不念哉。可不戒哉。愿明肃不以已得者自多。而须慥慥乎弗笃弗措之工。则宜自有德威重光。足以覃于朋友。如余之愚。亦庶几观感而警励焉。聊以是求益云。宛在亭记
余闻峤南胜赏。密城楼观为第一。而城北又有绝特之称。阳也池是已。池在华岳之阳。故得其名。其防堰之壮。与杭州钱塘之陂。可甲乙矣。广可数千亩。深不见底。未知何代何人之创筑。而粤自罗丽。为生民利泽之源。灌溉乎田者。殆数十里许也。池之左右。挺秀峰峦。峛崺环拥。中有五屿。菱葭被面。其外四堤。嘉木异卉。丛列成阴。吾未目钱塘之胜。而亦能有此否欤。昔在 宣庙时。安东权公讳三燮号鹤山居士。爱此之赏。乃卜居于池北位良村。以山巾野服。日逍遥于塘陂绿阴之畔。欲作一亭于水中之屿。名以宛在。屋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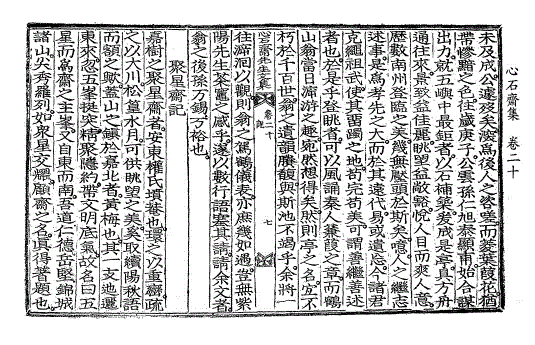 未及成。公遽殁矣。深为后人之咨嗟。而菱叶葭花。犹带惨黯之色。往岁庚子。公云孙仁旭泰显甫。始合谋出力。就五屿中最钜者。以石补筑。爰成是亭。具方舟通往来。景致益佳丽。眺望益敞豁。悦人目而爽人意。历数南州登临之美。几无压头于斯矣。噫。人之继志述事。是为孝先之大。而于其远代。易或遗忘。今诸君克绳祖武。使其留躅之地。苟完苟美。可谓善继善述者也。于是乎登眺者。可以风诵秦人蒹葭之章。而鹤山翁当日溯游之趣。宛然想得矣。然则亭之名。宜不朽于千百世。翁之遗韵剩馥。与斯池不竭乎。余将一往溯洄以观。则翁之驾鹤仪表。亦庶几如遇。岂无紫阳先生茶灶之感乎。遂以数行语塞其请。请余文者。翁之后孙万锡,万裕也。
未及成。公遽殁矣。深为后人之咨嗟。而菱叶葭花。犹带惨黯之色。往岁庚子。公云孙仁旭泰显甫。始合谋出力。就五屿中最钜者。以石补筑。爰成是亭。具方舟通往来。景致益佳丽。眺望益敞豁。悦人目而爽人意。历数南州登临之美。几无压头于斯矣。噫。人之继志述事。是为孝先之大。而于其远代。易或遗忘。今诸君克绳祖武。使其留躅之地。苟完苟美。可谓善继善述者也。于是乎登眺者。可以风诵秦人蒹葭之章。而鹤山翁当日溯游之趣。宛然想得矣。然则亭之名。宜不朽于千百世。翁之遗韵剩馥。与斯池不竭乎。余将一往溯洄以观。则翁之驾鹤仪表。亦庶几如遇。岂无紫阳先生茶灶之感乎。遂以数行语塞其请。请余文者。翁之后孙万锡,万裕也。聚星斋记
嘉树之聚星斋者。安东权氏坟庵也。环之以重峦。疏之以大川。松篁水月。可供眺望之美。奚取续阳秋语而额之欤。盖山之镇于嘉北者。黄梅也。其一支迤逦东来。忽五峰挺突。精聚隐约。带文明底气。故名曰五星而为斋之主峰。又自东而南。吾道,仁德,岳坚,锦城诸山。尖秀罗列。如众星交耀。顾斋之名。真得著题也。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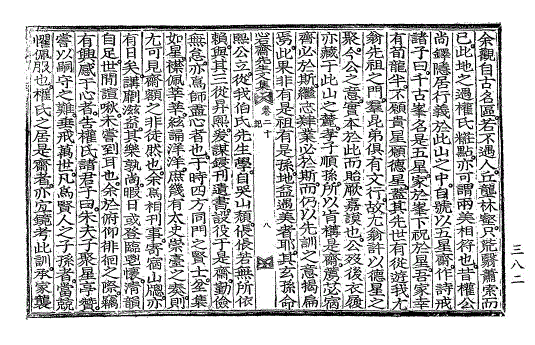 余观自古名区。若不遇人。丘垄林壑。只荒翳萧索而已。此地之遇权氏妆点。亦可谓两美相符也。昔权公尚铎隐居行义于此山之中。自号以五星斋。作诗戒诸子曰。千古峰名是五星。家于峰下祝于星。吾家幸有荀龙半。不愿贵星愿德星。盖其先世有从游我尤翁先祖之门。群昆弟俱有文行。故尤翁许以德星之聚。今公之意。实本于此而贻厥嘉谟也。公殁后衣履亦藏于此山之麓。孝子顺孙。所以肯构是斋。荐苾宿齐必于斯。继志肄业必于斯。而仍以先训之意揭扁焉。此果非有是祖有是孙。地益遇美者耶。其玄孙命熙公立。从我伯氏先生学。自哭山颓。伥伥若无所依赖。与其三从升熙。爰谋锓刊遗书。设役于是斋。勤俭无怠。亦为师尽心者也。于时四方同门之贤士。坌集如星。襟佩莘莘。弦诵洋洋。庶几有太史崇台之奏。则尤可见斋额之非徒然也。余为相刊事。寄宿山窗。亦有日矣。讲劘滋益。其乐孰尚。暇日或登临鬯怀。清韵自足。世閒諠啾。未尝到耳也。余于俯仰徘徊之际。窃有兴感于心者。告权氏诸君子曰。朱夫子聚星亭赞。尝以嗣守之难。垂戒万世。凡为贤人之子孙者。当兢惧佩服也。权氏之居是斋者。亦宜镜考此训。承家袭
余观自古名区。若不遇人。丘垄林壑。只荒翳萧索而已。此地之遇权氏妆点。亦可谓两美相符也。昔权公尚铎隐居行义于此山之中。自号以五星斋。作诗戒诸子曰。千古峰名是五星。家于峰下祝于星。吾家幸有荀龙半。不愿贵星愿德星。盖其先世有从游我尤翁先祖之门。群昆弟俱有文行。故尤翁许以德星之聚。今公之意。实本于此而贻厥嘉谟也。公殁后衣履亦藏于此山之麓。孝子顺孙。所以肯构是斋。荐苾宿齐必于斯。继志肄业必于斯。而仍以先训之意揭扁焉。此果非有是祖有是孙。地益遇美者耶。其玄孙命熙公立。从我伯氏先生学。自哭山颓。伥伥若无所依赖。与其三从升熙。爰谋锓刊遗书。设役于是斋。勤俭无怠。亦为师尽心者也。于时四方同门之贤士。坌集如星。襟佩莘莘。弦诵洋洋。庶几有太史崇台之奏。则尤可见斋额之非徒然也。余为相刊事。寄宿山窗。亦有日矣。讲劘滋益。其乐孰尚。暇日或登临鬯怀。清韵自足。世閒諠啾。未尝到耳也。余于俯仰徘徊之际。窃有兴感于心者。告权氏诸君子曰。朱夫子聚星亭赞。尝以嗣守之难。垂戒万世。凡为贤人之子孙者。当兢惧佩服也。权氏之居是斋者。亦宜镜考此训。承家袭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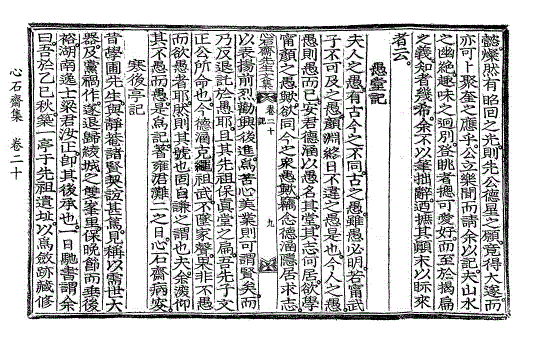 懿。灿然有昭回之光。则先公德星之愿。竟得大遂。而亦可卜聚奎之应乎。公立乐闻而请余以记。夫山水之幽绝。趣味之迥别。登眺者总可爱好。而至于揭扁之义。知者几希。余不以笔拙辞。乃摭其颠末以视来者云。
懿。灿然有昭回之光。则先公德星之愿。竟得大遂。而亦可卜聚奎之应乎。公立乐闻而请余以记。夫山水之幽绝。趣味之迥别。登眺者总可爱好。而至于揭扁之义。知者几希。余不以笔拙辞。乃摭其颠末以视来者云。愚堂记
夫人之愚。有古今之不同。古之愚。虽愚必明。若宁武子不可及之愚。颜渊终日不违之愚是也。今人之愚。愚则愚而已。安君德涵以愚名其堂。其志何居。欲学宁颜之愚欤。欲同今之众愚欤。窃念德涵隐居求志。以表扬前烈劝兴后进。为苦心美业则可谓贤矣。而乃反退托于愚耶。且其先祖保真堂之扁。吾先子文正公所命也。今德涵克绳祖武。不坠家声。果非不愚而欲愚者耶。然则其号也固自谦之谓也夫。余深仰其不愚而愚。是为记。著雍涒滩二之日。心石斋病叟。
寒后亭记
昔学圃先生。与静庵诸贤契谊甚笃。见称以需世大器。及党祸作。遂退归绫城之双峰里。保晚节而垂后裕。湖南逸士梁君汝正。即其后承也。一日驰书谓余曰。吾于乙巳秋。筑一亭于先祖遗址。以为敛迹藏修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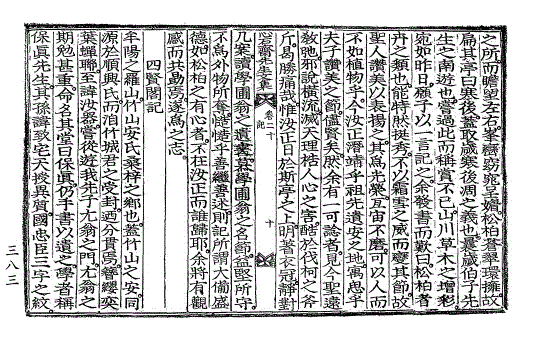 之所。而瞻望左右。峰峦窈窕呈媚。松柏苍翠环拥。故扁其亭曰寒后。盖取岁寒后凋之义也。曩岁伯子先生之南游也。尝过此而称赏不已。山川草木之增彩。宛如昨日。愿子以一言记之。余发书而叹曰。松柏者卉之类也。能特然挺秀。不以霜雪之威而变其节。故圣人赞美以表扬之。其为光荣。亘宙不磨。可以人而不如植物乎。今汝正潜靖乎祖先遗安之地。寓思乎夫子赞美之节。尽贤矣。然余有一可谂者。见今圣远教弛。邪说横流。灭天理梏人心之害。酷于伐柯之斧斤。曷胜痛哉。惟汝正日于斯亭之上。明著衣冠。静对几案。读学圃翁之遗文。慕学圃翁之名节。益坚所守。不为外物所夺。慥慥乎善继善述。则记所谓大备盛德。如松柏之有心者。不在汝正而谁归耶。余将有观感而共勖焉。遂为之志。
之所。而瞻望左右。峰峦窈窕呈媚。松柏苍翠环拥。故扁其亭曰寒后。盖取岁寒后凋之义也。曩岁伯子先生之南游也。尝过此而称赏不已。山川草木之增彩。宛如昨日。愿子以一言记之。余发书而叹曰。松柏者卉之类也。能特然挺秀。不以霜雪之威而变其节。故圣人赞美以表扬之。其为光荣。亘宙不磨。可以人而不如植物乎。今汝正潜靖乎祖先遗安之地。寓思乎夫子赞美之节。尽贤矣。然余有一可谂者。见今圣远教弛。邪说横流。灭天理梏人心之害。酷于伐柯之斧斤。曷胜痛哉。惟汝正日于斯亭之上。明著衣冠。静对几案。读学圃翁之遗文。慕学圃翁之名节。益坚所守。不为外物所夺。慥慥乎善继善述。则记所谓大备盛德。如松柏之有心者。不在汝正而谁归耶。余将有观感而共勖焉。遂为之志。四贤阁记
牟阳之罗山。竹山安氏桑梓之乡也。盖竹山之安。同源于顺兴氏。而洎竹城君之受封。乃分贯焉。簪缨奕叶蝉联。至讳汝器。尝从游我先子尤翁之门。尤翁之期勉甚重。命名其堂曰保真。仍手书以遗之。学者称保真先生。其孙讳致宅天授异质。国忠臣三字之纹。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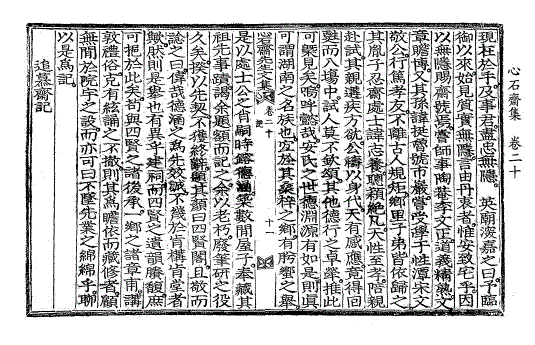 现在于手。及事君。尽忠无隐。 英庙深嘉之曰。予临御以来。始见质实无隐。言由丹衷者。惟安致宅乎。因以无隐赐斋号焉。尝师事陶庵李文正。道义精熟。文章赡博。又其孙讳挺鲁号市岩。尝受学于性潭宋文敬公。行笃孝友。不离古人规矩。乡里子弟皆依归之。其胤子忍斋处士讳志养。聪颖绝凡。天性至孝。陪亲赴试。其亲遘疾方㞃。公祷以身代。天有感应。竟得回苏而入场中。试人莫不钦颂。其他德行之卓荦。推此可槩见矣。呜呼懿哉。安氏之世德渊源有如是。则真可谓湖南之名族也。宜于其桑梓之乡。有肸蚃之举。是以处士公之肖嗣时镕德涵。筑数閒屋子。奉藏其祖先事迹。谒余题额而记之。余以老朽。废笔研之役久矣。揆以先契。不获终辞。题其颜曰四贤阁。且敬而谂之曰。伟哉德涵之为先效诚。不几于肯构肯堂者欤。然则是举也有异乎建祠。而四贤之遗韵剩馥。庶可挹于此矣。苟与四贤之诸后承。一乡之诸章甫。讲敦礼俗。克有弦诵之不撤。则其为瞻依而藏修者。顾无閒于院宇之设。而亦可曰不坠先业之绵绵乎。聊以是为记。
现在于手。及事君。尽忠无隐。 英庙深嘉之曰。予临御以来。始见质实无隐。言由丹衷者。惟安致宅乎。因以无隐赐斋号焉。尝师事陶庵李文正。道义精熟。文章赡博。又其孙讳挺鲁号市岩。尝受学于性潭宋文敬公。行笃孝友。不离古人规矩。乡里子弟皆依归之。其胤子忍斋处士讳志养。聪颖绝凡。天性至孝。陪亲赴试。其亲遘疾方㞃。公祷以身代。天有感应。竟得回苏而入场中。试人莫不钦颂。其他德行之卓荦。推此可槩见矣。呜呼懿哉。安氏之世德渊源有如是。则真可谓湖南之名族也。宜于其桑梓之乡。有肸蚃之举。是以处士公之肖嗣时镕德涵。筑数閒屋子。奉藏其祖先事迹。谒余题额而记之。余以老朽。废笔研之役久矣。揆以先契。不获终辞。题其颜曰四贤阁。且敬而谂之曰。伟哉德涵之为先效诚。不几于肯构肯堂者欤。然则是举也有异乎建祠。而四贤之遗韵剩馥。庶可挹于此矣。苟与四贤之诸后承。一乡之诸章甫。讲敦礼俗。克有弦诵之不撤。则其为瞻依而藏修者。顾无閒于院宇之设。而亦可曰不坠先业之绵绵乎。聊以是为记。追慕斋记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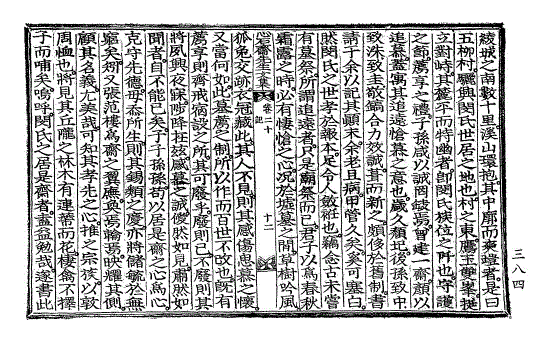 绫城之南数十里。溪山环抱。其中廓而爽垲者。是曰五柳村。骊兴闵氏世居之地也。村之东。鹰玉双峰。挺立对峙。其麓平而特幽者。即闵氏族位之阡也。守护之节。荐享之礼。子孙咸以诚罔缺焉。曾建一斋。颜以追慕。盖寓其追远怆慕之意也。岁久颓圮。后孙致中,致洙,致圭,敬镐合力效诚。葺而新之。颇侈于旧制。书请于余以记其颠末。余老且病。甲管久矣。奚可塞白。然闵氏之世孝于报本。足令人敛衽也。窃念古未尝有墓祭。所谓追远者。只是庙祭而已。君子以为春秋霜露之时。必有悽怆之心。况于墟墓之閒。草树吟风。狐兔交迹。衣冠藏此。其人不见。则其感伤思慕之怀。又当何如。此墓荐之制。所以作而百世不改也。既有荐享则齐戒宿设之所。其可废乎。废则已。不废则其将夙兴夜寐。陟降在玆。感慕之诚。僾然如见。肃然如闻者。自不能已矣。子子孙孙。苟以居是斋之心为心。克守先德。毋忝所生。则其锡类之庆。亦将储毓于无穷矣。矧又张范楼为斋之翼庑。奂焉轮焉。映耀其侧。顾其名义。尤美哉。可知其孝先之心。推之宗族。以敦周恤也。将见其丘陇之林木有连蒂而花。栖禽不择子而哺矣。呜呼。闵氏之居是齐者。盍益勉哉。遂书此
绫城之南数十里。溪山环抱。其中廓而爽垲者。是曰五柳村。骊兴闵氏世居之地也。村之东。鹰玉双峰。挺立对峙。其麓平而特幽者。即闵氏族位之阡也。守护之节。荐享之礼。子孙咸以诚罔缺焉。曾建一斋。颜以追慕。盖寓其追远怆慕之意也。岁久颓圮。后孙致中,致洙,致圭,敬镐合力效诚。葺而新之。颇侈于旧制。书请于余以记其颠末。余老且病。甲管久矣。奚可塞白。然闵氏之世孝于报本。足令人敛衽也。窃念古未尝有墓祭。所谓追远者。只是庙祭而已。君子以为春秋霜露之时。必有悽怆之心。况于墟墓之閒。草树吟风。狐兔交迹。衣冠藏此。其人不见。则其感伤思慕之怀。又当何如。此墓荐之制。所以作而百世不改也。既有荐享则齐戒宿设之所。其可废乎。废则已。不废则其将夙兴夜寐。陟降在玆。感慕之诚。僾然如见。肃然如闻者。自不能已矣。子子孙孙。苟以居是斋之心为心。克守先德。毋忝所生。则其锡类之庆。亦将储毓于无穷矣。矧又张范楼为斋之翼庑。奂焉轮焉。映耀其侧。顾其名义。尤美哉。可知其孝先之心。推之宗族。以敦周恤也。将见其丘陇之林木有连蒂而花。栖禽不择子而哺矣。呜呼。闵氏之居是齐者。盍益勉哉。遂书此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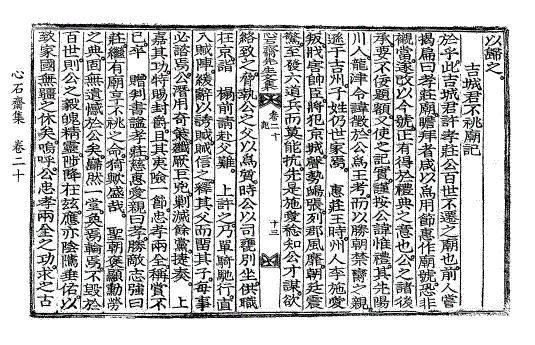 以归之。
以归之。吉城君不祧庙记
于乎。此吉城君许孝庄公百世不迁之庙也。前人尝揭扁曰孝庄庙。瞻拜者咸以为用节惠作庙号。恐非衬当。遂改以今号。正有得于礼典之意也。公之诸后承。要不佞题额。又使之记实。谨按公讳惟礼。其先阳川人。龙津令讳徵。于公为王考。而以胜朝禁脔之亲。逊于吉州。子姓仍世家焉。 惠庄王时。州人李施爱叛。戕害帅臣。将犯京城。声势鸱张。列郡风靡。朝廷震惊。至发六道兵而莫能抗。先是施爱稔知公才谋。欲络致之。胁执公之父以为质。时公以司瓮别坐。供职在京。诣 榻前请赴父难。 上许之。乃单骑驰行。直入贼阵。缓辞以诱贼。贼信之。释其父而留其子。每事必咨焉。公潜用奇策。歼厥巨凶。剿灭馀党。捷奏。 上嘉其功。特赐封爵。且其夷险一节。忠孝两全。称赏不已。卒 赠判书谥孝庄。慈惠爱亲曰孝。胜敌志强曰庄。继有庙享不祧之命。猗欤盛哉。 圣朝褒显勋劳之典。固无遗憾于公矣。岿然一堂。奂焉轮焉。不毁于百世。则公之毅魄精灵。陟降在玆。应亦阴骘垂佑。以致家国无疆之休矣。呜呼。公忠孝两全之功。求之古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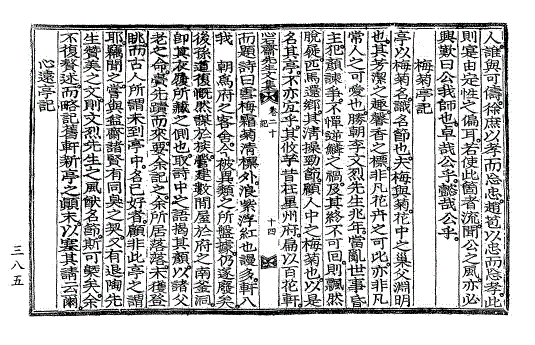 人。谁与可俦。徐庶以孝而忘忠。赵苞以忠而忘孝。此则寔由定性之偏耳。若使此个者流。闻公之风。亦必兴叹曰公我师也。卓哉公乎。懿哉公乎。
人。谁与可俦。徐庶以孝而忘忠。赵苞以忠而忘孝。此则寔由定性之偏耳。若使此个者流。闻公之风。亦必兴叹曰公我师也。卓哉公乎。懿哉公乎。梅菊亭记
亭以梅菊名。识名节也。夫梅与菊。花中之巢父渊明也。其芳洁之趣。馨香之标。非凡花卉之可比。亦非凡常人之可爱也。胜朝李文烈先生兆年。当乱世事昏主。犯颜谏争。不惮逆鳞之祸。及其终不可回。则飘然脱屣。匹马还乡。其清操劲节。顾人中之梅菊也。以是名其亭。不亦宜乎。其攸芋昔在星州府。扁以百花轩。而题诗曰雪梅霜菊清标外。浪紫浮红也谩多。轩入我 朝为府之客舍。今被异类之所盘据。仍遂废矣。后孙道复慨然谋于族。营建数閒屋于府之南釜洞。即其衣履所藏之侧也。取诗中之语揭其颜。以诸父老之命。赍先迹而来。要余记之。余所居落落。未获登眺。而古人所谓未到亭中。名已好者。顾非此亭之谓耶。窃闻之。尝与益斋诸贤有同臭之契。又有退陶先生赞美之文。则文烈先生之风猷名节。斯可槩矣。余不复赘述。而略记旧轩新亭之颠末。以塞其请云尔。
心远亭记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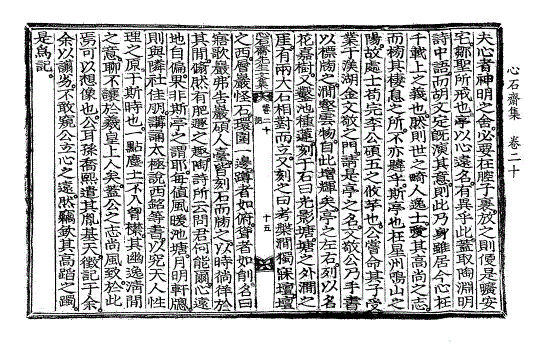 夫心者神明之舍。必要在腔子里。放之则便是旷安宅。邹圣所戒也。亭以心远名。有异乎此。盖取陶渊明诗中语。而胡文定既演其意。则此乃身虽居今心在千载上之义也。然则世之畸人逸士。爱其高尚之志。而榜其栖息之所。不亦韪乎。斯亭也在星州鸣山之阳。故处士苟完李公硕五之攸芋也。公尝命其子受业于渼湖金文敬之门。请是亭之名。文敬公乃手书以标榜之。涧壑云物。自此增辉矣。亭之左右。列以名花嘉树。又凿池种莲。刻于石曰光影塘。塘之外涧之厓。有两大石相对而立。又刻之曰考槃涧独寐坛。坛之西。层岩怪石。环围一边。蹲者如俯。耸者如削。名曰寤歌岩,弗告岩,硕人台。皆刻石而榜之。以时徜徉于其閒。翛然有肥遁之趣。陶诗所云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果非斯亭之谓耶。每值风暖池塘。月明轩窗。则与邻社佳朋。讲诵太极说,西铭等书。以究天人性理之原。于斯时也。一点尘土不入胸襟。其幽逸清閒之意。聊不让于羲皇上人矣。盖公之志尚风致。于此焉可以想像也。公耳孙乔熙遣其胤基天。徵记于余。余以谫劣。不敢窥公立心之远。然窃钦其高蹈之躅。是为记。
夫心者神明之舍。必要在腔子里。放之则便是旷安宅。邹圣所戒也。亭以心远名。有异乎此。盖取陶渊明诗中语。而胡文定既演其意。则此乃身虽居今心在千载上之义也。然则世之畸人逸士。爱其高尚之志。而榜其栖息之所。不亦韪乎。斯亭也在星州鸣山之阳。故处士苟完李公硕五之攸芋也。公尝命其子受业于渼湖金文敬之门。请是亭之名。文敬公乃手书以标榜之。涧壑云物。自此增辉矣。亭之左右。列以名花嘉树。又凿池种莲。刻于石曰光影塘。塘之外涧之厓。有两大石相对而立。又刻之曰考槃涧独寐坛。坛之西。层岩怪石。环围一边。蹲者如俯。耸者如削。名曰寤歌岩,弗告岩,硕人台。皆刻石而榜之。以时徜徉于其閒。翛然有肥遁之趣。陶诗所云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果非斯亭之谓耶。每值风暖池塘。月明轩窗。则与邻社佳朋。讲诵太极说,西铭等书。以究天人性理之原。于斯时也。一点尘土不入胸襟。其幽逸清閒之意。聊不让于羲皇上人矣。盖公之志尚风致。于此焉可以想像也。公耳孙乔熙遣其胤基天。徵记于余。余以谫劣。不敢窥公立心之远。然窃钦其高蹈之躅。是为记。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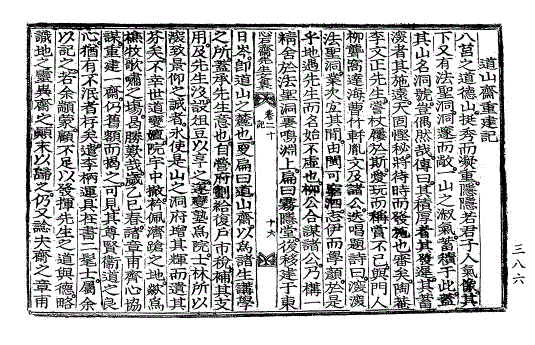 道山斋重建记
道山斋重建记八莒之道德山。挺秀而凝重。隐隐若君子人气像。其下又有法圣洞。洞邃而敞。一山之淑气。蓄积于此。盖其山名洞号。岂偶然哉。传曰。其积厚者其发迟。其蓄深者其施远。天固悭秘。将待时而发施也审矣。陶庵李文正先生。尝杖屦于斯。爱玩而称赏不已。与门人柳聋窝达海,曹竹轩胤文及诸公。迭唱题诗曰。深深法圣洞。业次宜其閒。由闽可穷泗。志伊而学颜。于是乎地遇先生而名始不虚也。柳公合谋诸公。乃构一精舍于法圣洞里鸣渊上。扁曰雾隐堂。后移建于东日岑。即道山之麓也。更扁曰道山斋。以为诸生讲学之所。盖承先生意也。自营府划给复户市税。补其支用。及先生没。设俎豆以享之。遂变塾为院。士林所以深致景仰之诚者。永使是山之洞府增其辉而遗其芬矣。不幸世道变嬗。院宇中撤。衿佩济跄之地。歘为樵牧歌啸之场。曷胜叹哉。岁乙巳春。诸章甫齐心协谋。重建一斋。仍旧额而揭之。可见其尊贤卫道之良心。犹有不泯者存矣。遣李柄运,具在书二髦士。属余以记之。若余颛蒙。顾不足以发挥先生之道与德。略识地之灵异斋之颠末以归之。仍又谂夫斋之章甫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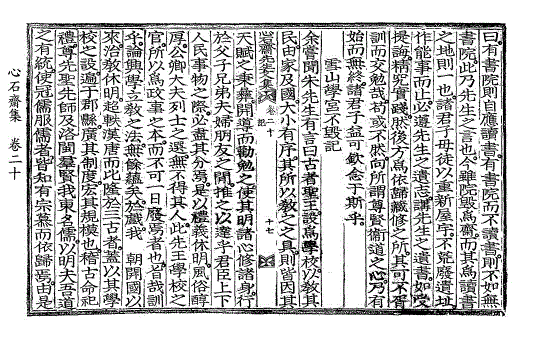 曰。有书院则自应读书。有书院而不读书。则不如无书院。此乃先生之言也。今虽院毁为斋。而其为读书之地则一也。诸君子毋徒以重新屋宇。不荒废遗址。作能事而止。必遵先生之遗志。讲先生之遗书。如受提诲。精究实践。然后方为依归藏修之所。其可不胥训而交勉哉。苟或不然。向所谓尊贤卫道之心。乃有始而无终。诸君子益可钦念于斯乎。
曰。有书院则自应读书。有书院而不读书。则不如无书院。此乃先生之言也。今虽院毁为斋。而其为读书之地则一也。诸君子毋徒以重新屋宇。不荒废遗址。作能事而止。必遵先生之遗志。讲先生之遗书。如受提诲。精究实践。然后方为依归藏修之所。其可不胥训而交勉哉。苟或不然。向所谓尊贤卫道之心。乃有始而无终。诸君子益可钦念于斯乎。雪山学宫不毁记
余尝闻朱先生有言曰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閒。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尽其分焉。是以礼义休明。风俗醇厚。公卿大夫列士之选。无不得其人。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而不可一日废焉者也。旨哉训乎。论兴学立教之法。无馀蕴矣。于戏。我 朝开国以来。治教休明。超轶汉唐而比隆于三古者。盖以其学校之设。遍于郡县。广其制度。宏其规模也。稽古命祀礼。尊先圣先师及洛闽群贤我东名儒。以明夫吾道之有统。使冠儒服儒者。皆知有宗慕而依归焉。由是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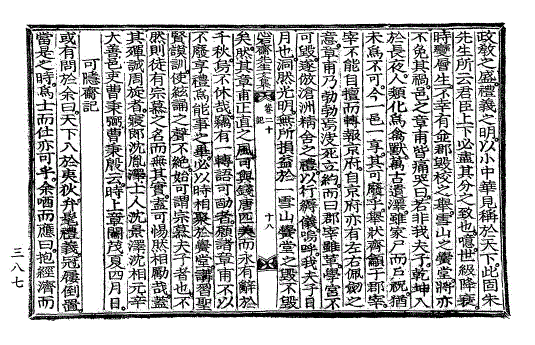 政教之盛。礼义之明。以小中华见称于天下。此固朱先生所云君臣上下必尽其分之致也。噫。世级降衰。时变层生。不幸有并郡毁校之举。雪山之黉堂。将亦不免其祸。邑之章甫皆痛哭曰。若非我夫子。乾坤入于长夜。人类化为禽兽。万古遗泽。虽家尸而户祝。犹未为不可。今一邑一享。其可废乎。举状齐龥于郡宰。宰不能自擅而转报京府。自京府亦有左右佩剑之意。章甫乃勃勃焉决死立约。而曰郡宰虽革。学宫不可毁。遂仿沧洲精舍之礼。以行缛仪。呜呼。我夫子日月也。洞然光明。无所损益于一雪山黉堂之毁不毁矣。然其章甫正直之风。可与钱唐匹美而永有辞于千秋。乌不休哉。窃有一转语可勔者。愿诸章甫不以不废享礼为能事之毕。必以时相聚于黉堂。讲习圣贤谟训。使弦诵之声不绝。始可谓宗慕夫子者也。不然则徒有宗慕之名而无其实。盍可惕然相励哉。盖其殚诚周旋者。寝郎沈胤泽,士人沈景泽,沈相元,辛大善,邑吏曹秉弼,曹秉殷云。时上章阉茂夏四月日。
政教之盛。礼义之明。以小中华见称于天下。此固朱先生所云君臣上下必尽其分之致也。噫。世级降衰。时变层生。不幸有并郡毁校之举。雪山之黉堂。将亦不免其祸。邑之章甫皆痛哭曰。若非我夫子。乾坤入于长夜。人类化为禽兽。万古遗泽。虽家尸而户祝。犹未为不可。今一邑一享。其可废乎。举状齐龥于郡宰。宰不能自擅而转报京府。自京府亦有左右佩剑之意。章甫乃勃勃焉决死立约。而曰郡宰虽革。学宫不可毁。遂仿沧洲精舍之礼。以行缛仪。呜呼。我夫子日月也。洞然光明。无所损益于一雪山黉堂之毁不毁矣。然其章甫正直之风。可与钱唐匹美而永有辞于千秋。乌不休哉。窃有一转语可勔者。愿诸章甫不以不废享礼为能事之毕。必以时相聚于黉堂。讲习圣贤谟训。使弦诵之声不绝。始可谓宗慕夫子者也。不然则徒有宗慕之名而无其实。盍可惕然相励哉。盖其殚诚周旋者。寝郎沈胤泽,士人沈景泽,沈相元,辛大善,邑吏曹秉弼,曹秉殷云。时上章阉茂夏四月日。可隐斋记
或有问于余曰。天下入于夷狄。弁髦礼义。冠屦倒置。当是之时。为士而仕亦可乎。余哂而应曰。抱经济而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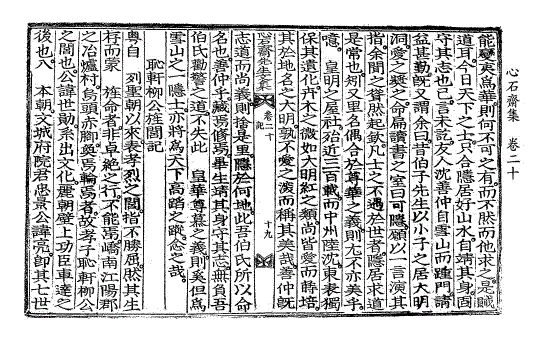 能变夷为华。则何不可之有。而不然而他求之。是贼道耳。今日天下之士。只合隐居好山水。自靖其身。固守其志也已。言未讫。友人沈善仲自雪山而踵门。请益甚勤。既又谓余曰。昔伯子先生以小子之居大明洞。爱之奖之。命扁读书之室曰可隐。愿以一言演其指。余闻之耸然起钦。凡士之不遇于世者。隐居求道是常也。矧又里名偶合于尊华之义。则尤不亦美乎。噫。 皇明之屋社。殆近三百载。而中州陆沈。东表独保其遗化。卉木之微如大明红之类。尚皆爱而莳培。其于地名之大明。孰不爱之深而称其美哉。善仲既志道而尚义。则舍是里。隐于何地。此吾伯氏所以命名也。善仲乎。藏焉修焉。毕生靖其身守其志。无负吾伯氏劝警之道。不失此 皇华尊慕之义。则奚但为雪山之一隐士。亦将为天下高蹈之踪。念之哉。
能变夷为华。则何不可之有。而不然而他求之。是贼道耳。今日天下之士。只合隐居好山水。自靖其身。固守其志也已。言未讫。友人沈善仲自雪山而踵门。请益甚勤。既又谓余曰。昔伯子先生以小子之居大明洞。爱之奖之。命扁读书之室曰可隐。愿以一言演其指。余闻之耸然起钦。凡士之不遇于世者。隐居求道是常也。矧又里名偶合于尊华之义。则尤不亦美乎。噫。 皇明之屋社。殆近三百载。而中州陆沈。东表独保其遗化。卉木之微如大明红之类。尚皆爱而莳培。其于地名之大明。孰不爱之深而称其美哉。善仲既志道而尚义。则舍是里。隐于何地。此吾伯氏所以命名也。善仲乎。藏焉修焉。毕生靖其身守其志。无负吾伯氏劝警之道。不失此 皇华尊慕之义。则奚但为雪山之一隐士。亦将为天下高蹈之踪。念之哉。耻轩柳公旌闾记
粤自 列圣朝以来。表孝烈之闾。指不胜屈。然其生存而蒙 旌命者。非卓绝之行。不能焉。峤南江阳郡之冶炉村。乌头赤脚。奂焉轮焉者。故孝子耻轩柳公之闾也。公讳世勋。系出文化。丽朝壁上功臣车达之后也。入 本朝。文城府院君忠景公讳亮。即其七世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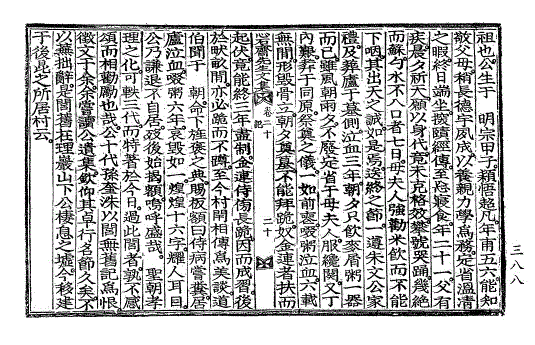 祖也。公生于 明宗甲子。颖悟超凡。年甫五六。能知敬父母。稍长德宇夙成。以养亲力学为务。定省温凊之暇。终日端坐。探赜经传。至忘寝食。年二十一。父有疾。晨夕祈天。愿以身代。竟未克格效。攀号哭踊。几绝而苏。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母夫人强劝米饮而不能下咽。其出天之诚。如是焉。送终之节。一遵朱文公家礼。及葬庐于墓侧。泣血三年。朝夕只饮麦屑粥一器而已。虽风朝雨夕。不废定省于母夫人。服才阕。又丁内艰。葬于同原。祭奠之仪。一如前丧。啜粥泣血。六载无閒。形毁骨立。朝夕奠墓。不能拜跪。奴金连者扶而起伏。竟能终三年尽制。金连侍傍长跪。因而成习。后于畎亩閒。亦必跪而不蹲。至今村闬相传为美谈。道伯闻于 朝。命下旌褒之典。赐板额曰侍病尝粪。居庐泣血。啜粥六年。哀毁如一。煌煌十六字。耀人耳目。公乃谦退不自居。殁后始揭额。呜呼盛哉。 圣朝孝理之化。可轶三代。而特著于今日。过此闾者。孰不感颂而相劝励也哉。公十代孙奎洙以闾无旧记为恨。徵文于余。余尝读公遗集。钦仰其卓行名节久矣。不以芜拙辞。是闾旧在理岩山下公栖息之墟。今移建于后昆之所居村云。
祖也。公生于 明宗甲子。颖悟超凡。年甫五六。能知敬父母。稍长德宇夙成。以养亲力学为务。定省温凊之暇。终日端坐。探赜经传。至忘寝食。年二十一。父有疾。晨夕祈天。愿以身代。竟未克格效。攀号哭踊。几绝而苏。勺水不入口者七日。母夫人强劝米饮而不能下咽。其出天之诚。如是焉。送终之节。一遵朱文公家礼。及葬庐于墓侧。泣血三年。朝夕只饮麦屑粥一器而已。虽风朝雨夕。不废定省于母夫人。服才阕。又丁内艰。葬于同原。祭奠之仪。一如前丧。啜粥泣血。六载无閒。形毁骨立。朝夕奠墓。不能拜跪。奴金连者扶而起伏。竟能终三年尽制。金连侍傍长跪。因而成习。后于畎亩閒。亦必跪而不蹲。至今村闬相传为美谈。道伯闻于 朝。命下旌褒之典。赐板额曰侍病尝粪。居庐泣血。啜粥六年。哀毁如一。煌煌十六字。耀人耳目。公乃谦退不自居。殁后始揭额。呜呼盛哉。 圣朝孝理之化。可轶三代。而特著于今日。过此闾者。孰不感颂而相劝励也哉。公十代孙奎洙以闾无旧记为恨。徵文于余。余尝读公遗集。钦仰其卓行名节久矣。不以芜拙辞。是闾旧在理岩山下公栖息之墟。今移建于后昆之所居村云。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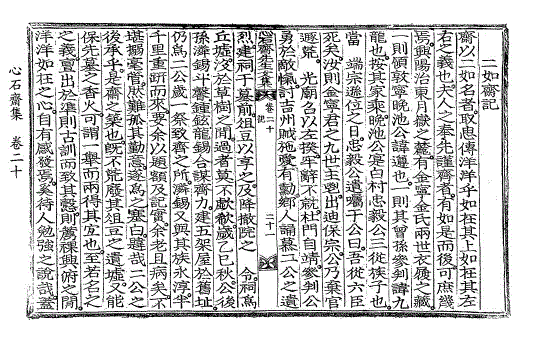 二如斋记
二如斋记斋以二如名者。取思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义也。夫人之奉先谨齐者。有如是而后。可庶几焉。兴阳治东月岳之麓。有金宁金氏两世衣履之藏。一则领敦宁晚池公讳遵也。一则其曾孙参判讳九龙也。按其家乘。晚池公寔白村忠毅公三从族子也。当 端宗逊位之日。忠毅公遗嘱于公曰。吾从六臣死矣。汝则金宁君之九世主鬯。出迪保宗。公乃弃官遁荒。 光庙召以左揆。牢辞不就。杜门自靖。参判公勇于敌忾。讨吉州贼施爱有勋。乡人诵慕二公之遗烈。建祠于墓前。俎豆以享之。及降撤院之 令。祠为丘墟。没于草树之閒。过者莫不歔欷。岁乙巳秋。公后孙潾锡,斗馨,钟铉,龙锡合谋齐力。建五架屋于旧址。仍为二公岁一祭致齐之所。潾锡又与其族永淳。半千里重趼而来。要余以题额及记实。余老且病矣。不堪搦毫管。然难孤其勤意。遂为之塞白。韪哉二公之后承乎。是斋之筑也。既不荒废其俎豆之遗墟。又能保先墓之香火。可谓一举而两得其宜也。至若名之之义。亶出于准则古训而致其悫。则荐祼兴俯之閒。洋洋如在之心。自有感发焉。奚待人勉强之说哉。盖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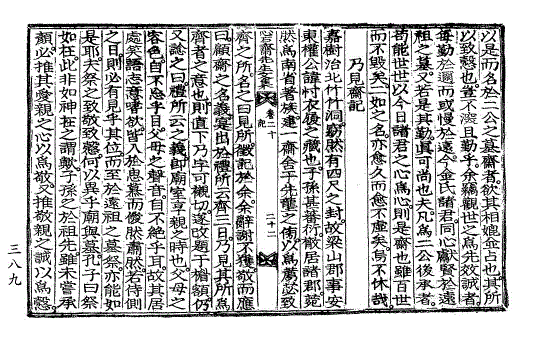 以是而名于二公之墓斋者。欲其相媲并占也。其所以致壳也。岂不深且勤乎。余窃观世之为先效诚者。每勤于迩而或慢于远。今金氏诸君。同心献贤于远祖之墓。又若是其勤。真可尚也夫。凡为二公后承者。苟能世世以今日诸君之心为心。则是斋也虽百世而不毁矣。二如之名。亦愈久而愈不虚矣。乌不休哉。
以是而名于二公之墓斋者。欲其相媲并占也。其所以致壳也。岂不深且勤乎。余窃观世之为先效诚者。每勤于迩而或慢于远。今金氏诸君。同心献贤于远祖之墓。又若是其勤。真可尚也夫。凡为二公后承者。苟能世世以今日诸君之心为心。则是斋也虽百世而不毁矣。二如之名。亦愈久而愈不虚矣。乌不休哉。乃见斋记
嘉树治北竹竹洞。窈然有四尺之封。故梁山郡事安东权公讳忖衣履之藏也。子孙甚蕃衍。散居诸郡。菀然为南省著族。建一斋舍于先垄之傍。以为荐苾致齐之所。名之曰见所。徵记于余。余辞谢不获。敬而应曰。顾斋之名义。寔出于礼所云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之意也。则直下乃字可衬切。遂改题于楣额。仍又谂之曰。礼所云之义。即庙室享亲之时也。父母之容色。自不忘乎目。父母之声音。自不绝乎耳。故其居处笑语志意嗜欲。皆入于思慕而僾然肃然。若侍侧之日。则必有见乎其位。而至于远祖之墓祭。亦能如是耶。夫祭之致敬致悫。何以异乎庙与墓。孔子曰祭如在。此非如神在之谓欤。子孙之于祖先。虽未尝承颜。必推其爱亲之心以为敬。又推敬亲之诚以为悫。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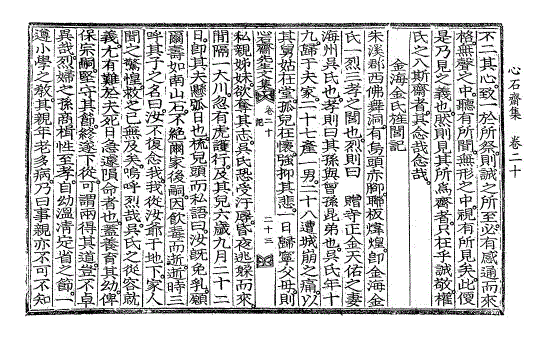 不二其心。致一于所祭。则诚之所至。必有感通而来格。无声之中。听有所闻。无形之中。视有所见矣。此便是乃见之义也。然则见其所为齐者。只在乎诚敬。权氏之入斯斋者。其念哉念哉。
不二其心。致一于所祭。则诚之所至。必有感通而来格。无声之中。听有所闻。无形之中。视有所见矣。此便是乃见之义也。然则见其所为齐者。只在乎诚敬。权氏之入斯斋者。其念哉念哉。金海金氏旌闾记
朱溪郡西佛舞洞。有乌头赤脚。联板炜煌。即金海金氏一烈三孝之闾也。烈则曰 赠寺正金天佑之妻海州吴氏也。孝则曰其孙与曾孙昆弟也。吴氏年十九。归于夫家。二十七产一男。二十八遭城崩之痛。以其舅姑在堂。孤儿在怀。强抑其悲。一日归宁父母。则私亲姊妹。欲夺其志。吴氏恐受污辱。昏夜逃躲而来。閒隔一大川。忽有虎护行。及其儿六岁九月二十二日。即其夫悬弧日也。梳儿头而私语曰。汝既免乳。愿尔寿如南山石。不绝尔家后嗣。因饮毒而逝。逝时三呼其子之名曰。汝不复念我。我从汝爷于地下。家人闻之惊惶。救之已无及矣。呜呼烈哉。吴氏之从容就义。尤有难于夫死日急遽陨命者也。盖养育其幼。俾保宗嗣。坚守其节。终遂下从。可谓两得其道。岂不卓异哉。烈妇之孙商楫性至孝。自幼温凊定省之节。一遵小学之教。其亲年老多病。乃曰事亲亦不可不知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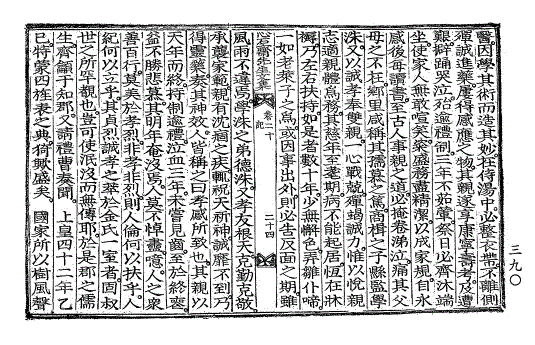 医。因学其术而造其妙。在侍汤中。必整衣带。不离侧殚诚进药。屡得感应之物。其亲遂享康宁寿考。及遭艰。擗踊哭泣。殆逾礼制。三年不茹荤。祭日必齐沐端坐。使家人无敢喧笑。粢盛务尽精洁。以成家规。自永感后每读书。至古人事亲之道。必掩卷涕泣。痛其父母之不在。乡里咸称其孺慕之笃。商楫之子县监学洙。又以诚孝奉双亲。一心战兢。殚竭诚力。惟以悦亲志适亲体为务。其慈年至耄期。病不能起居。恒在床褥。乃左右扶持。如是者数十年。少无懈色。弄雏仆啼。一如老莱子之为。或因事出外。则必告反面之期。虽风雨不违焉。学洙之弟德洙。又孝友根天。克勤克敬。承袭家范。亲有沈痼之疾。辄祝天祈神。诚靡不到。乃得灵药。奏其神效。人皆称之曰孝感所致也。其亲以天年而终。持制逾礼。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至于终丧。益不胜悲慕。其明年奄没焉。人莫不悼衋。噫。人之众善百行。莫美于孝烈。非孝非烈。则人伦何以扶乎。人纪何以立乎。其贞烈诚孝之萃于金氏一室者。固叔世之所罕睹也。岂可使泯没而无传耶。于是郡之儒生。齐龥于知郡。又请礼曹奏闻。 上皇四十二年乙巳。特蒙四旌表之典。猗欤盛矣。 国家所以树风声
医。因学其术而造其妙。在侍汤中。必整衣带。不离侧殚诚进药。屡得感应之物。其亲遂享康宁寿考。及遭艰。擗踊哭泣。殆逾礼制。三年不茹荤。祭日必齐沐端坐。使家人无敢喧笑。粢盛务尽精洁。以成家规。自永感后每读书。至古人事亲之道。必掩卷涕泣。痛其父母之不在。乡里咸称其孺慕之笃。商楫之子县监学洙。又以诚孝奉双亲。一心战兢。殚竭诚力。惟以悦亲志适亲体为务。其慈年至耄期。病不能起居。恒在床褥。乃左右扶持。如是者数十年。少无懈色。弄雏仆啼。一如老莱子之为。或因事出外。则必告反面之期。虽风雨不违焉。学洙之弟德洙。又孝友根天。克勤克敬。承袭家范。亲有沈痼之疾。辄祝天祈神。诚靡不到。乃得灵药。奏其神效。人皆称之曰孝感所致也。其亲以天年而终。持制逾礼。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至于终丧。益不胜悲慕。其明年奄没焉。人莫不悼衋。噫。人之众善百行。莫美于孝烈。非孝非烈。则人伦何以扶乎。人纪何以立乎。其贞烈诚孝之萃于金氏一室者。固叔世之所罕睹也。岂可使泯没而无传耶。于是郡之儒生。齐龥于知郡。又请礼曹奏闻。 上皇四十二年乙巳。特蒙四旌表之典。猗欤盛矣。 国家所以树风声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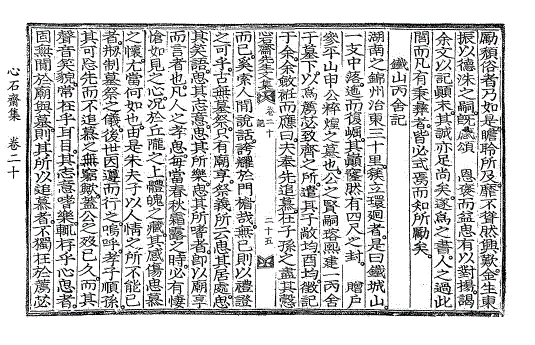 励颓俗者乃如是。瞻聆所及。靡不耸然兴叹。金生东振以德洙之嗣。既感颂 恩褒而益思有以对扬。谒余文以记颠末。其诚亦足尚矣。遂为之书。人之过此闾而凡有秉彝者。皆必式焉而知所励矣。
励颓俗者乃如是。瞻聆所及。靡不耸然兴叹。金生东振以德洙之嗣。既感颂 恩褒而益思有以对扬。谒余文以记颠末。其诚亦足尚矣。遂为之书。人之过此闾而凡有秉彝者。皆必式焉而知所励矣。铁山丙舍记
湖南之锦州治东三十里。簇立环回者。是曰铁城山。一支中落。迤而复崛。其巅窿然有四尺之封。 赠户参平山申公粹煌之墓也。公之贤嗣瑢熙建一丙舍于墓下。以为荐苾致齐之所。遣其子敞均,酉均。徵记于余。余敛衽而应曰。夫奉先追慕。在子孙之尽其悫而已。奚索人閒说话。誇耀于门楣哉。无已则以礼證之可乎。古无墓祭。只有庙享。祭义所云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者。即以庙享而言者也。凡人之孝思。每当春秋霜露之时。必有悽怆如见之心。况于丘陇之上体魄之藏。其感伤思慕之怀。尤当何如也。由是朱夫子以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刱制墓祭之仪。后世因遵而行之。呜呼。孝子顺孙。其可忘先而不追慕之无穷欤。盖公之殁已久。而其声音笑貌。常在乎耳目。其志意嗜乐。辄存乎心思者。固无閒于庙与墓。则其所以追慕者。不独在于荐苾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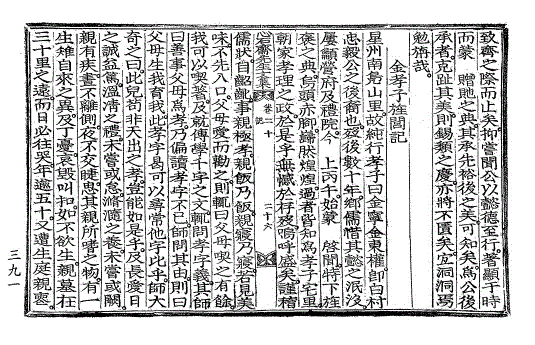 致齐之际而止矣。抑尝闻公以懿德至行。著显于时而蒙 赠貤之典。其承先裕后之美。可知矣。为公后承者。克趾其美。则锡类之庆。亦将不匮矣。宜洞洞焉勉旃哉。
致齐之际而止矣。抑尝闻公以懿德至行。著显于时而蒙 赠貤之典。其承先裕后之美。可知矣。为公后承者。克趾其美。则锡类之庆。亦将不匮矣。宜洞洞焉勉旃哉。金孝子旌闾记
星州南凫山里。故纯行孝子曰金宁金东权。即白村忠毅公之后裔也。殁后数十年。乡儒惜其懿之泯没。屡龥营府及礼院。今 上丙午。始蒙 启闻。特下旌褒之典。乌头赤脚。岿然煌煌。过者皆知为孝子宅里。朝家孝理之政。于是乎无憾于存殁。呜呼盛矣。谨稽儒状。自龆龀。事亲极孝。亲饭乃饭。亲寝乃寝。若见美味。不先入口。父母爱而劝之。则辄曰父母吃之有馀。我可以吃著。及就傅学千字之文。辄问孝字义。其师曰善事父母为孝。乃偏读孝字不已。师问其由。则曰父母生我育我。此孝字曷可以寻常他字比乎。师大奇之曰。此儿苟非天出之孝。岂能如是乎。及长爱日之诚益笃。温凊之礼。未尝或怠。滫瀡之养。未尝或阙。亲有疾。昼不离侧。夜不交睫。思其亲所嗜之物。有一生雉自来之异。及丁忧。哀毁叫扣。如不欲生。亲墓在三十里之远。而日必往哭。年逾五十。又遭生庭亲丧。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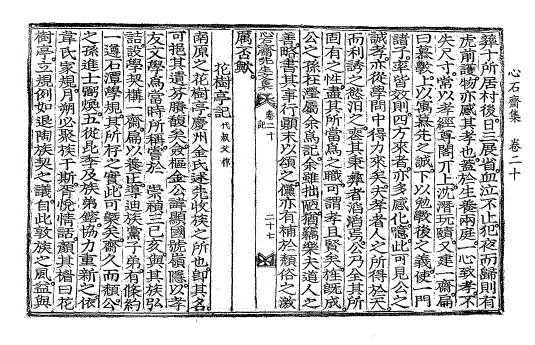 葬于所居村后。日三展省。血泣不止。犯夜而归则有虎前护。物亦感其孝也。盖于生养两庭。一心致孝。不失尺寸。常以孝经尊阁丌上。沈潜玩赜。又建一斋。扁曰慕敩。上以寓慕先之诚。下以勉敩后之义。使一门诸子。率皆效则。四方来者。亦多感化。噫。此可见公之诚孝。亦从学问中得力来矣。夫孝者人之所得于天。而利诱之欲汩之。丧其秉彝者滔滔焉。公乃全其所固有之性。尽其所当为之职。可谓孝且贤矣。旌既成。公之孙在滢属余为记。余虽拙陋。犹窃乐夫道人之善。略书其事行颠末以颂之。傥亦有补于颓俗之激厉否欤。
葬于所居村后。日三展省。血泣不止。犯夜而归则有虎前护。物亦感其孝也。盖于生养两庭。一心致孝。不失尺寸。常以孝经尊阁丌上。沈潜玩赜。又建一斋。扁曰慕敩。上以寓慕先之诚。下以勉敩后之义。使一门诸子。率皆效则。四方来者。亦多感化。噫。此可见公之诚孝。亦从学问中得力来矣。夫孝者人之所得于天。而利诱之欲汩之。丧其秉彝者滔滔焉。公乃全其所固有之性。尽其所当为之职。可谓孝且贤矣。旌既成。公之孙在滢属余为记。余虽拙陋。犹窃乐夫道人之善。略书其事行颠末以颂之。傥亦有补于颓俗之激厉否欤。花树亭记(代叔父作)
南原之花树亭。庆州金氏述先收族之所也。即其名。可挹其遗芬剩馥矣。佥枢金公讳显国号岭隐。以孝友文学为当时所称。尝于 崇祯三己亥。与其族弘诘。设学契构一斋。扁以养正。导迪族党子弟。有条约一遵石潭学规。其所存之实。此可槩矣。斋久而颓。公之孙进士弼焕。五从昆季及族弟镕。协力重新之。依韦氏家规。月朔必聚族于斯。胥悦情话。颜其楣曰花树亭。立规例如退陶族契之议。自此敦族之风。益与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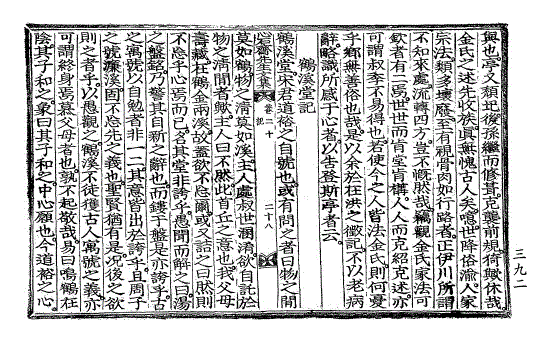 与也。亭又颓圮。后孙继而修葺。克袭前规。猗欤休哉。金氏之述先收族。真无愧古人矣。噫。世降俗渝。人家宗法。类多坏废。至有视骨肉如行路者。正伊川所谓不知来处。流转四方。岂不慨然哉。窃观金氏家法可钦者有二焉。世世而肯堂肯构。人人而克绍克述。亦可谓叔季不易得也。若使今之人皆法金氏。则何忧乎乡无善俗也哉。是以余于在洪之徵记。不以老病辞。略识所感于心者。以告登斯亭者云。
与也。亭又颓圮。后孙继而修葺。克袭前规。猗欤休哉。金氏之述先收族。真无愧古人矣。噫。世降俗渝。人家宗法。类多坏废。至有视骨肉如行路者。正伊川所谓不知来处。流转四方。岂不慨然哉。窃观金氏家法可钦者有二焉。世世而肯堂肯构。人人而克绍克述。亦可谓叔季不易得也。若使今之人皆法金氏。则何忧乎乡无善俗也哉。是以余于在洪之徵记。不以老病辞。略识所感于心者。以告登斯亭者云。鹤溪堂记
鹤溪堂。宋君道裕之自号也。或有问之者曰物之閒莫如鹤。物之清莫如溪。主人处叔世溷淆。欲自托于物之清閒者欤。主人曰不然。此首丘之意也。我父母寿藏。在鹤金两溪。故盖欲不忘尔。或又诘之曰然则不忘乎心焉而已。名其堂非誇乎。愚闻而解之曰。汤之盘铭。乃警其自新之辞也。而镂于盘是亦誇乎。古之寓号以自勉者非一二。其意皆出于誇乎。且周子之号濂溪。固不忘先之义也。圣贤犹有是。况后之欲则之者乎。以愚观之。鹤溪不徒获古人寓号之义。亦可谓终身焉慕父母者也。孰不起敬哉。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今道裕之心。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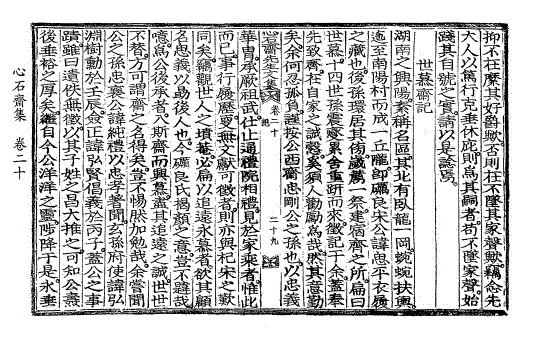 抑不在縻其好爵欤。否则在不坠其家声欤。窃念先大人以笃行克垂休庇。则为其嗣者。苟不坠家声。始践其自号之实。请以是谂焉。
抑不在縻其好爵欤。否则在不坠其家声欤。窃念先大人以笃行克垂休庇。则为其嗣者。苟不坠家声。始践其自号之实。请以是谂焉。世慕斋记
湖南之兴阳。素称名区。其北有卧龙一冈。蜿蜿扶舆。迤至南阳村而成一丘陇。即砺良宋公讳思平衣履之藏也。后孙环居其傍。岁荐一祭。建宿齐之所。扁曰世慕。十四世孙震燮累舍重趼而来。徵记于余。盖奉先致齐。在自家之诚悫。奚须人劝励为哉。然其意勤矣。余何忍孤负。谨按公西斋忠刚公之孙也。以忠义华胄。承厥祖武。仕止通礼院相礼。见于家乘者。惟此而已。事行履历。更无文献可徵者。则亦与杞宋之叹同矣。窃观世人之坟庵。必扁以追远永慕者。欲其顾名思义以勖后人也。今砺良氏揭颜之意。岂不韪哉。噫。为公后承者。入斯斋而兴慕。尽其追远之诚。世世不替。方可谓斋之名得矣。岂不惕然加勉哉。余尝闻公之孙忠襄公讳纯礼以忠孝著闻。玄孙府使讳弘渊树勋于壬辰。佥正讳弘贤倡义于丙子。盖公之事迹。虽曰遗佚无徵。以其子姓之昌大推之。可知公焘后垂裕之厚矣。继自今公洋洋之灵。陟降于是。永垂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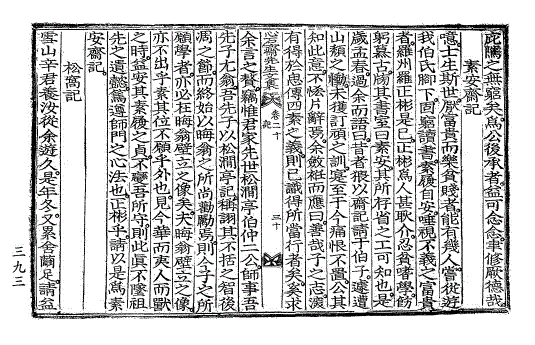 庇骘之无穷矣。为公后承者。益可念念。聿修厥德哉。
庇骘之无穷矣。为公后承者。益可念念。聿修厥德哉。素安斋记
噫。士生斯世。厌富贵而乐贫贱者。能有几人。尝从游我伯氏脚下。固穷读书。素履自安。唾视不义之富贵者。罗州罗正彬是已。正彬为人甚耿介。忍贫嗜学。饬躬慕古。榜其书室曰素安。其所存省之工可知也。是岁孟春。过余而语曰。昔者猥以斋记请于伯子。遽遭山颓之恸。未获订顽之训。寔至于今痛恨不置。公其知此意。不吝片辞焉。余敛衽而应曰。善哉子之志。深有得于思传四素之义。则已识得所当行者矣。奚求余言之赘。窃惟君家先世松涧亭伯仲二公。师事吾先子尤翁。吾先子以松涧亭记。称诩其不括之智后凋之节。而终始以晦翁之所尚劝励焉。则今子之所愿学者。亦必在晦翁壁立之像矣。夫晦翁壁立之像。亦不出乎素其位不愿乎外也。见今华而夷人而兽之时。益安其素履之贞。不变吾所守。则此真不坠祖先之遗懿。笃遵师门之心法也。正彬乎。请以是为素安斋记。
松窝记
雪山辛君养汝从余游久。是年冬。又累舍茧足。请益
心石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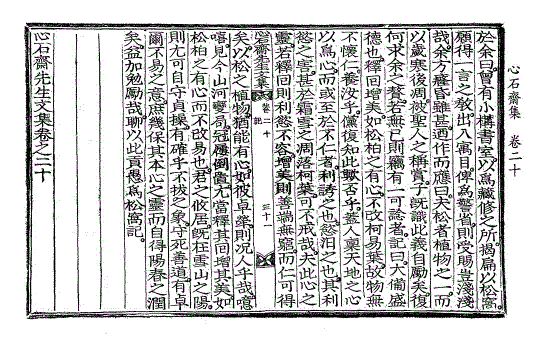 于余曰。曾有小构书室。以为藏修之所。揭扁以松窝。愿得一言之教。出入寓目。俾为警省。则受赐岂浅浅哉。余方癃昏虽甚。乃作而应曰。夫松者植物之一。而以岁寒后凋。被圣人之称赏。子既识此义自励矣。复何求余之赘。若无已则窃有一可谂者。记曰。大备盛德也。释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易叶。故物无不怀仁。养汝乎。傥复知此欤否乎。盖人禀天地之心以为心。而或至于不仁者。利诱之也。欲汩之也。其利欲之害。甚于霜雪之凋落柯叶。可不戒哉。夫此心之灵。若释回则利欲不容。增美则善端无穷。而仁可得矣。以松之植物。犹能有心。如彼卓荦。则况人乎哉。噫嘻。见今山河变局。冠屦倒置。尤当释其回增其美。如松柏之有心而不改易也。君之攸居。既在雪山之阳。则尤可自守贞操。有确乎不拔之象。守死善道。有卓尔不易之意。庶几保其本心之灵而自得阳春之润矣。益加勉励哉。聊以此贡愚为松窝记。
于余曰。曾有小构书室。以为藏修之所。揭扁以松窝。愿得一言之教。出入寓目。俾为警省。则受赐岂浅浅哉。余方癃昏虽甚。乃作而应曰。夫松者植物之一。而以岁寒后凋。被圣人之称赏。子既识此义自励矣。复何求余之赘。若无已则窃有一可谂者。记曰。大备盛德也。释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易叶。故物无不怀仁。养汝乎。傥复知此欤否乎。盖人禀天地之心以为心。而或至于不仁者。利诱之也。欲汩之也。其利欲之害。甚于霜雪之凋落柯叶。可不戒哉。夫此心之灵。若释回则利欲不容。增美则善端无穷。而仁可得矣。以松之植物。犹能有心。如彼卓荦。则况人乎哉。噫嘻。见今山河变局。冠屦倒置。尤当释其回增其美。如松柏之有心而不改易也。君之攸居。既在雪山之阳。则尤可自守贞操。有确乎不拔之象。守死善道。有卓尔不易之意。庶几保其本心之灵而自得阳春之润矣。益加勉励哉。聊以此贡愚为松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