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记
记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2H 页
 归隐洞记(己未)
归隐洞记(己未)达城府南数十里最顶山下有寒泉洞。洞府穹邃。岩石磊叠。中流一大川。川上有泉。泉甘而清冽。故名之以寒泉。余尝爱其名而书刻于石。寒泉西十许里。冈峦周遭。境幽而势衍。其山可以樵。其水可以钓。其土可以耕。曰云谷。又行六七里。断岩层嶂。清流白石。曲曲奇绝。无一不可意者。是之谓梅溪。溪上有村。曰梅南。梅之人多得年。有父子兄弟之龄之七八九十者在在矣。尝往游焉。有一老叟童发儿齿。视眸炯炯。殆不似烟火界中人。叩其年。其回甲之年。即吾生之乙酉。而筋力尚健矍。又不知将享几年寿。甚可异也。其南即琵瑟山之涌泉洞。亦有水石之胜。昔先师梅翁之送我行也。有诗曰。琵瑟山中辟洞天。龙迥凤跃涌灵泉。可怜匏系无因解。虚负名区八十年。又曰。龙蛇幽蛰自存身。桂树南山更可人。玉洞梅花应不老。欲飞云屩去寻春。肃斋赵公又书赠梅南二字而有所期勉。是则余何敢当。然亦不容不自勉也。凡此数地。皆深藏不市之士。所可盘桓而永矢不告者。而寒泉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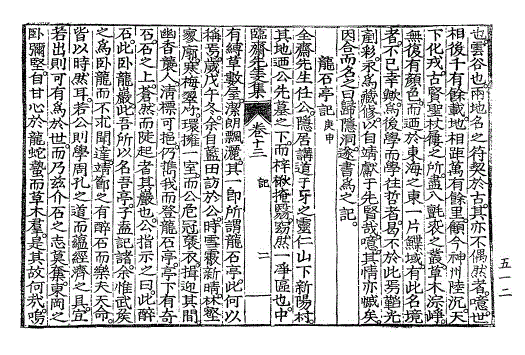 也。云谷也。两地名之符契于古。其亦不偶然者。噫。世相后千有馀载。地相距万有馀里。顾今神州陆沉。天下化戎。古贤圣杖屦之所。尽入毡裘之丛。草木淙峥。无复有颜色。而乃于东海之东一片鲽域。有此名境者。不已幸欤。为后学而学往哲者。曷不于此焉韬光铲彩。永为藏修。以自靖献于先贤哉。噫。其情亦戚矣。因合而名之曰归隐洞。遂书为之记。
也。云谷也。两地名之符契于古。其亦不偶然者。噫。世相后千有馀载。地相距万有馀里。顾今神州陆沉。天下化戎。古贤圣杖屦之所。尽入毡裘之丛。草木淙峥。无复有颜色。而乃于东海之东一片鲽域。有此名境者。不已幸欤。为后学而学往哲者。曷不于此焉韬光铲彩。永为藏修。以自靖献于先贤哉。噫。其情亦戚矣。因合而名之曰归隐洞。遂书为之记。龙石亭记(庚申)
全斋先生任公。隐居讲道于牙之灵仁山下新阳村。其地乃公先墓之下。而梓楸掩翳。窈然一净区也。中有缚草数屋。洁朗飘洒。其一即所谓龙石亭。此何以称焉。岁戊午冬。余自蓝田访于公。时雪霰新晴。林壑寥廓。寒梅翠竹。环拥一室。而公危冠袖衣。揖迎其间。幽香袭人。清标可挹。仍携我而登龙石亭。亭下有奇石。石之上。苍然而陡起者其岩也。公指示之曰。此醉石。此卧龙岩。此吾所以名吾亭。子盍记诸。余惟武侯之为卧龙而不求闻达。靖节之有醉石而乐夫天命。皆以时然耳。若公则学周孔之道而蕴经济之具。宜若出则可有为于世。而乃玆介石之志莫夺。东冈之卧弥坚。自甘心于龙蛇蛰而草木群。是其故何哉。呜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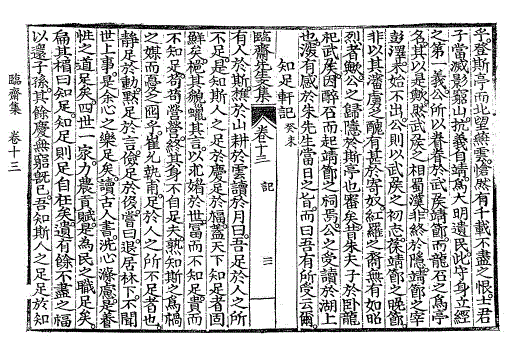 乎。登斯亭而北望燕云。怆然有千载不尽之恨。士君子当灭影穷山。抗义自靖。为大明遗民。此守身立经之第一义。公所以眷眷于武侯靖节。而龙石之为亭名。其以是欤。然武侯之相蜀汉。非终于隐。靖节之宰彭泽。未始不出。公则以武侯之初志。葆靖节之晚节。非以其沈虏之丑有甚于寄奴。红罗之裔无有如昭烈者欤。公之归隐于斯亭也审矣。昔朱夫子于卧龙祀武侯。因醉石而起靖节之祠焉。公之受读于湖上也。深有感于朱先生当日之旨。而曰吾有所受云尔。
乎。登斯亭而北望燕云。怆然有千载不尽之恨。士君子当灭影穷山。抗义自靖。为大明遗民。此守身立经之第一义。公所以眷眷于武侯靖节。而龙石之为亭名。其以是欤。然武侯之相蜀汉。非终于隐。靖节之宰彭泽。未始不出。公则以武侯之初志。葆靖节之晚节。非以其沈虏之丑有甚于寄奴。红罗之裔无有如昭烈者欤。公之归隐于斯亭也审矣。昔朱夫子于卧龙祀武侯。因醉石而起靖节之祠焉。公之受读于湖上也。深有感于朱先生当日之旨。而曰吾有所受云尔。知足轩记(癸未)
有人于斯。樵于山耕于云读于月曰。吾足于人之所不足。是知斯人之足于庆足于福。盖天下知足者固鲜矣。栀其貌蜡其言。以求媚于世。富而不知足。贵而不知足。苟苟营营。终其身不自足夫。熟知斯之为祸之媒而忧之囮乎。崔允执甫。足于人之所不足者也。静足于动。默足于言。俭足于侈。尝曰。退居林下。不闻世上事。是余心之乐足矣。读古人书。洗心涤虑。是养性之道足矣。四世一家。力农贡赋。是为民之职足矣。扁其楣曰知足。知足则足自在矣。遗有馀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其馀庆无穷既已。吾知斯人之足足于知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3L 页
 足。是为说。
足。是为说。灵曜楼记
达治东十里琴湖上。南望三峰崒嵂。其俨然处而伛偻如抱者曰母峰。双峙列立如左右侍者曰兄弟峰也。友人夏锡圭甫。兄弟三人隐居其下。而养母夫人孝。其先公教官公尝有至行。盖以孝友世其家者也。然尝闻教官公平日旨物之诚得以自尽者。盖亦得之内助者居多。今其诸子之孝友有称。倘非如申国夫人教诲之如此其严欤。然则夫人即向所谓俨然处之母峰。而其诸子者。乃左右侍之兄弟峰欤。灵淑之气。渟萃其一家焉者。可异焉。灵曜楼者。夫人起居之室。是迂里李尚书所命名而挥染者也。尚书不轻与人。而与锡圭甫游好。且以灵曜二字用替寿嘏之辞。俾揭诸萱楣。是其意必艳钦于闺范庭模。而抑亦勉其所不及。以及古人之至者耶。锡圭甫尝要余一言记其事。顾不文。无以阐发其义。而有终不能辞者。乃举其所居山名之不偶然者。明其为母为兄弟各得自尽其道者。以有钟毓之所由致。而百灵输福。七曜降禄。将徵其未艾无涯之庆于玆楼云尔。
起龙斋记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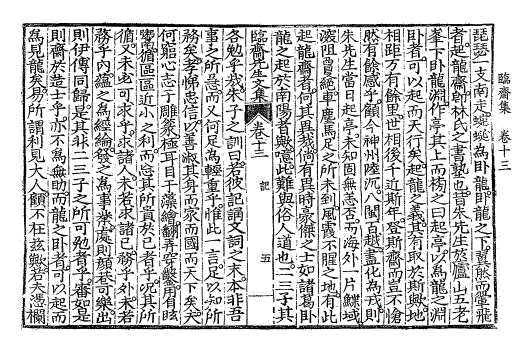 琵瑟一支南走。蜿蜒为卧龙。卧龙之下。翼然而翚飞者。起龙斋。即林氏之书塾也。昔朱先生于庐山五老峰下卧龙渊。作亭其上而榜之曰起亭。以为龙之渊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起龙之义。其有取于斯欤。地相距万有馀里。世相后千近斯年。登斯斋而岂不怆然有馀感乎。顾今神州陆沉。八闽百越。尽化为戎。则朱先生当日起亭。未知固无恙否。而海外一片鲽域。深阻夐绝。车尘马足之所未到。风霞不腥之地。有此起龙斋者。何其异哉。倘有异时豪杰之士如诸葛卧龙之起于南阳者欤。噫。此难与俗人道也。二三子其各勉乎哉。朱子之训曰。若彼记诵文词之末。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为轻重乎。惟此一言。足以知所务矣。孝悌忠信。以善淑其身而家而国而天下矣。夫何穷心志于雕篆。极耳目于藻绘。翻弄穿凿。用自眩鬻。循区区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贵于己者乎。况其所循。又未必可求乎。求诸人。未若求诸己。务乎外。未若务乎内。蕴之为经纶。发之为事业。处则颜巷可乐。出则伊傅同归。是其非二三子之所可勉者乎。审如是则斋于造士乎。亦不为无助。而龙之卧者。可以起而为见龙矣。易所谓利见大人。顾不在玆欤。若夫凭栏
琵瑟一支南走。蜿蜒为卧龙。卧龙之下。翼然而翚飞者。起龙斋。即林氏之书塾也。昔朱先生于庐山五老峰下卧龙渊。作亭其上而榜之曰起亭。以为龙之渊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起龙之义。其有取于斯欤。地相距万有馀里。世相后千近斯年。登斯斋而岂不怆然有馀感乎。顾今神州陆沉。八闽百越。尽化为戎。则朱先生当日起亭。未知固无恙否。而海外一片鲽域。深阻夐绝。车尘马足之所未到。风霞不腥之地。有此起龙斋者。何其异哉。倘有异时豪杰之士如诸葛卧龙之起于南阳者欤。噫。此难与俗人道也。二三子其各勉乎哉。朱子之训曰。若彼记诵文词之末。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为轻重乎。惟此一言。足以知所务矣。孝悌忠信。以善淑其身而家而国而天下矣。夫何穷心志于雕篆。极耳目于藻绘。翻弄穿凿。用自眩鬻。循区区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贵于己者乎。况其所循。又未必可求乎。求诸人。未若求诸己。务乎外。未若务乎内。蕴之为经纶。发之为事业。处则颜巷可乐。出则伊傅同归。是其非二三子之所可勉者乎。审如是则斋于造士乎。亦不为无助。而龙之卧者。可以起而为见龙矣。易所谓利见大人。顾不在玆欤。若夫凭栏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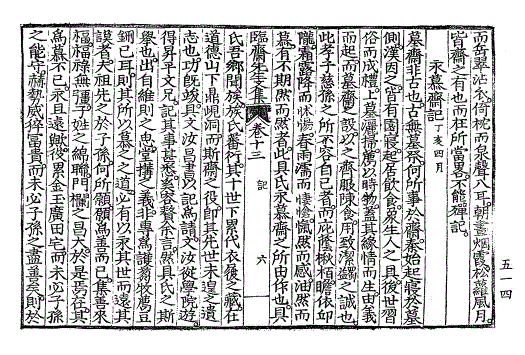 而岳翠沾衣。倚枕而泉声入耳。朝昼烟霞。松萝风月。皆斋之有也而在所当略。不能殚记。
而岳翠沾衣。倚枕而泉声入耳。朝昼烟霞。松萝风月。皆斋之有也而在所当略。不能殚记。永慕斋记(丁亥四月)
墓斋非古也。古无墓祭。何所事于斋。秦始起寝于墓侧。汉因之。皆有园寝。起居饮食。象生人之具。后世习俗而成礼。上墓洒扫。荐以时物。盖其缘情而生。由义而起。而墓斋之设。以之齐服陈食。用致洁蠲之诚也。此孝子慈孙之所不容自已者。而庇荫楸柏。瞻依邱陇。霜露降而怵惕。春雨濡而悽怆。忾然而感。油然而慕。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具氏永慕斋之所由作也。具氏吾乡闻族。族氏蕃衍。其十世下累代衣履之藏。在道德山下鼎岘洞。而斯斋之役。即其先世未遑之遗志也。功既竣。具文汝昌书以记为请。文汝从学院游。得升平文兄。记其事甚悉。奚容赘余言。然具氏之斯举也。出自维则之思。堂搆之义。非专为护刍牧荐豆铏已耳。则其所以慕之之道。必有以永其世而远其谟者。夫祖先之于子孙。何所愿。愿为善而已。集善来福。福禄无彊。子姓之绵联。门栏之昌大。于是焉在。其为慕不已。永且远欤。彼累金玉广田宅。而未必子孙之能守。赫势威猝富贵。而未必子孙之尽善矣。则于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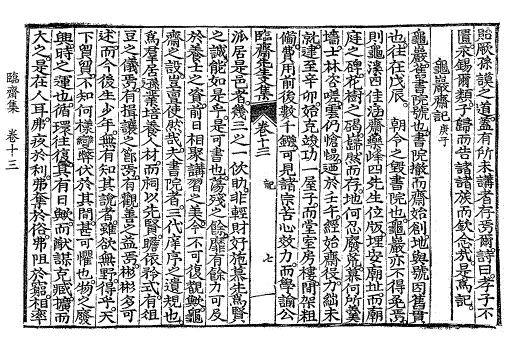 贻厥孙谟之道。盖有所未讲者存焉尔。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子归而告诸诸族而钦念哉。是为记。
贻厥孙谟之道。盖有所未讲者存焉尔。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子归而告诸诸族而钦念哉。是为记。龟岩斋记(庚子)
龟岩。旧书院号也。书院撤而斋始创。地与号因旧贯也。往在戊辰。 朝令之毁书院也。龟岩亦不得免焉。则龟溪,四佳,涵斋,药峰四先生位版。埋安庙址。而庙庭之碑。花树之碣。岿然而存。地何忍废荒。慕何所羹墙。士林咨嗟。云仍怆惕。乃于壬午。经始斋役。力绌未就。逮至辛卯。始克竣功一屋子。而堂室房楼。间架粗备。费用前后数千镪。可见诸宗苦心效力。而学谕公派居是邑者。几三之一佽助。非轻财好施慕先为贤之诚。能如是乎。是可书也。荡残之馀。靡有馀力可及于养士之资。前日相聚讲习之美。今不可复睹欤。龟斋之设。岂亶使然哉。夫书院者。三代庠序之遗规也。为群居逊业培养人材。而祠以先贤。瞻依矜式。有俎豆之仪焉。有揖让之节焉。有观善之益焉。彬彬多可述。而今后生少年。无有知其说者。虽欲无野。得乎。天下贸贸。不知何样变弊伏于其间。甚可惧也。物之废兴。时之运也。循环往复。其有日欤。而猷谋克臧。扩而大之。是在人耳。弗疚于利。弗夺于俗。弗阻于穷。相率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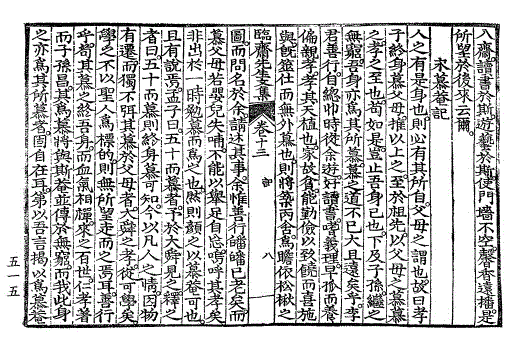 入斋。读书于斯。游艺于斯。使门墙不空。馨香远播。是所望于后来云尔。
入斋。读书于斯。游艺于斯。使门墙不空。馨香远播。是所望于后来云尔。永慕庵记
人之有是身也。则必有其所自。父母之谓也。故曰孝子终身慕父母。推以上之。至于祖先。以父母之慕慕之。孝之至也。苟如是。岂止吾身已也。下及子孙。继之无穷。吾身亦为其所慕。慕之道不已大且远矣乎。李君善行。自总丱时从余游。好读书。嗜义理。早孤而养偏亲孝。孝其天植也。家故贫。能勤俭以致饶而喜施与。既筮仕而无外慕也。则将筑丙舍。为瞻依松楸之图。而问名于余。请述其事。余惟善行皤皤已老矣。而慕父母若婴儿失哺。不能以举足自忘。呜呼其孝矣。非出于一时勉慕而为之也。然则颜之以慕庵可也。且有说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释之者曰。五十而慕则终身慕可知。今以凡人之情。因物有迁。而独不弭其慕于父母者。大舜之孝。从可学矣。学之不以圣人为标的。则无所望走而之焉耳。善行乎。苟其慕之终吾身。而血气相禅。来之百世。仁孝著而子孙昌。其为慕将与斯庵并传于无穷。而我此身之亦为其所慕者。固自在耳。第以吾言揭以为慕庵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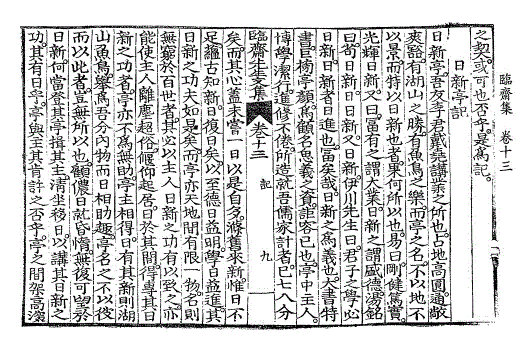 之契。或可也否乎。是为记。
之契。或可也否乎。是为记。日新亭记
日新亭。吾友李君戴尧讲业之所也。占地高圆。通敞爽豁。有湖山之胜。有鱼鸟之乐。而亭之名。不以地不以景。而特以日新也者。果何所以也。易曰。刚健笃实。光辉日新。又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汤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川先生曰。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富矣哉。日新之为义也。大书特书。巨榜亭颜。为顾名思义之资。讵容已也。亭中主人。博学洁行。进修不倦。所造就吾儒家计者。已七八分矣。而其心盖未尝一日以是自多。涤旧来新。惟日不足。蕴古知新。日复日矣。以至德日益明。学日益进。其日新之功夫如是矣。而亭亦天地间有限一物。名则无穷于百世者。其必以主人日新之功有以致之。亦能使主人离尘超俗。偃仰起居。日于其间。得专其日新之功者。亭亦不为无助。亭主相得。日有其新则湖山鱼鸟。举为吾分内物而日相助趣。亭名之不以彼而以此者。岂无所以也。顾侬日就昏惰。无复可望于日新。何当登其亭揖其主。清坐移日。以讲其日新之功。其有日乎。亭与主其肯许之否乎。亭之间架高深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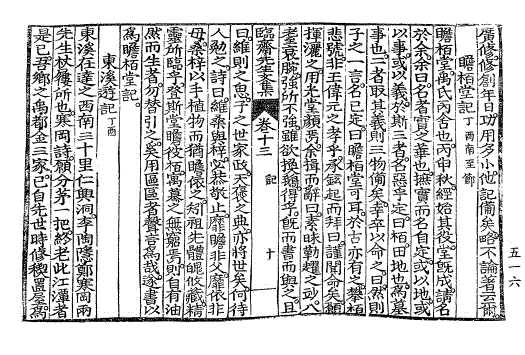 广修。修创年日。功用多小。他记备矣。略不论著云尔。
广修。修创年日。功用多小。他记备矣。略不论著云尔。瞻柏堂记(丁酉南至节)
瞻柏堂。禹氏丙舍也。丙申秋。经始其役。堂既成。请名于余。余曰。名者实之华也。摭实而名自定。或以地。或以事。或以义。于斯三者。名恶乎定。曰柏。田地也。为墓事也。二者取其义则三物备矣。幸卒以命之。曰。然则子之一言。名已定。曰瞻柏堂可耳。于古亦有之。攀柏悲号。非王伟元之孝乎。承铉起而拜曰。谨闻命矣。愿挥洒之。用光堂颜焉。余揖而辞曰。素昧勒趯之妙。八耋衰腕。强所不强。虽欲换鹅。得乎。既而书而与之。且曰。维则之思。子之世家政。天褒之典。亦将世矣。何待人勉之。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非父。靡依非母。桑梓以手植物而犹瞻依之。矧祖先体魄攸藏。精灵所临乎。登斯堂瞻彼柏。寓慕之无穷焉。则自有油然而生者。勿替引之。奚用区区者声言为哉。遂书以为瞻柏堂记。
东溪游记(丁酉)
东溪在达之西南三十里仁兴洞。李陶隐,郑寒冈两先生杖屦所也。寒冈诗。愿分茅一把。终老此江潭者是已。吾乡之禹,都,金三家。已自先世时修稧置屋。为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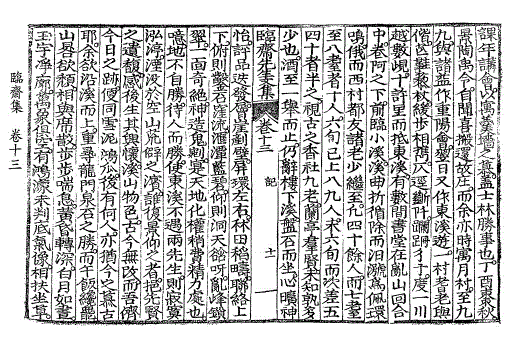 课年讲会。以寓羹墙之慕。盖士林胜事也。丁酉枣秋。景陶禹令。自闻喜搬还故庄。而余亦时寓月村。至九九。与诸益作重阳会。翌日又作东溪游。一村耆老与偕。芒鞋藜杖。缓步相携。仄径断阡。躝跚彳亍。度一川越数岘。十许里而抵东溪。有数间书堂在乱山回合中。卷阿之下。前临小溪。溪曲折循除而汩𤂆为佩环鸣。俄而西村都友诸老少继至。凡四十馀人。而七耋至八耋者十人。六旬已上八九人。未六旬而次差五四十者半之。视古之香社九老。兰亭群贤。未知孰多少也。酒至一举而止。仍辞楼下溪。盘石而坐。心旷神怡。评品迭发。层崖铲壁。屏环左右。秫田稻畴。联络上下。俯则凿石洼流。汇潭蓝碧。仰则洞天谽呀。乱峰锁翠。一面奇绝。神造鬼剜。寔天地化权稍费精力处也。噫。地不自胜。待人而胜。使东溪不遇两先生。则寂寞泓渟。湮没于空山荒僻之滨。谁复景仰之者。挹先贤之遗馥。感后生其兴怀。溪山物色。古今无改。而吾侪今日之迹。便同雪泥鸿爪。后有何人。亦犹今之慕古耶。余欲沿溪而上。重寻龙门泉石之胜。而午饭才罢。山晷欲颓。相与席散。步步喘息。黄昏转深。白月如昼。玉宇净廓。万象俱空。有鸿濛未判底气像。相扶坐草。
课年讲会。以寓羹墙之慕。盖士林胜事也。丁酉枣秋。景陶禹令。自闻喜搬还故庄。而余亦时寓月村。至九九。与诸益作重阳会。翌日又作东溪游。一村耆老与偕。芒鞋藜杖。缓步相携。仄径断阡。躝跚彳亍。度一川越数岘。十许里而抵东溪。有数间书堂在乱山回合中。卷阿之下。前临小溪。溪曲折循除而汩𤂆为佩环鸣。俄而西村都友诸老少继至。凡四十馀人。而七耋至八耋者十人。六旬已上八九人。未六旬而次差五四十者半之。视古之香社九老。兰亭群贤。未知孰多少也。酒至一举而止。仍辞楼下溪。盘石而坐。心旷神怡。评品迭发。层崖铲壁。屏环左右。秫田稻畴。联络上下。俯则凿石洼流。汇潭蓝碧。仰则洞天谽呀。乱峰锁翠。一面奇绝。神造鬼剜。寔天地化权稍费精力处也。噫。地不自胜。待人而胜。使东溪不遇两先生。则寂寞泓渟。湮没于空山荒僻之滨。谁复景仰之者。挹先贤之遗馥。感后生其兴怀。溪山物色。古今无改。而吾侪今日之迹。便同雪泥鸿爪。后有何人。亦犹今之慕古耶。余欲沿溪而上。重寻龙门泉石之胜。而午饭才罢。山晷欲颓。相与席散。步步喘息。黄昏转深。白月如昼。玉宇净廓。万象俱空。有鸿濛未判底气像。相扶坐草。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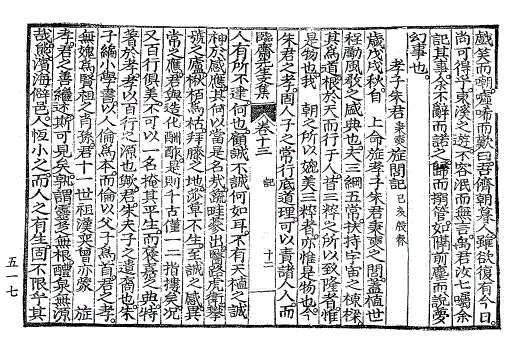 戏笑而嘲。嘘唏而叹曰。吾侪朝暮人。虽欲复有今日。尚可得乎。东溪之游。不容泯而无言。禹君汝七嘱余记其事。余不辞而诺之。归而搦管。如隔前尘而说梦幻事也。
戏笑而嘲。嘘唏而叹曰。吾侪朝暮人。虽欲复有今日。尚可得乎。东溪之游。不容泯而无言。禹君汝七嘱余记其事。余不辞而诺之。归而搦管。如隔前尘而说梦幻事也。孝子朱君(秉奭)旌闾记(己亥殷春)
岁戊戌秋。自 上命旌孝子朱君秉奭之闾。盖植世程励风教之盛典也。夫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梁。其为道。根于天而行于人。昔三粹之所以致隆者。惟是物也。我 朝之所以媲美三粹者。亦惟是物也。今朱君之孝。固人子之常行底道理。可以责诸人人。而人有所不逮。何也。顾诚不诚何如耳。不有天植之诚神于感应。其何以当是名哉。蔬畦蔘出。医路虎卫。攀号之庐。楸柏为枯。拜膝之地。莎草不生。至诚之感。异常之应。君与造化酬酢。是则千古仅一二指搂矣。况又百行俱美。不可以一名掩其平生。而褒嘉之典。特著于孝。孝以百行之源也欤。君。朱夫子之遗裔也。朱子编小学书。以人伦为本。而伦以父子为首。君之孝。无愧为贤祖之肖孙。君十一世祖汉奕曾亦蒙 旌孝。君之善继述。斯可见矣。孰谓灵芝无根。醴泉无源哉。熊。滨海僻邑。人恒小之。而人之有生。固不限乎其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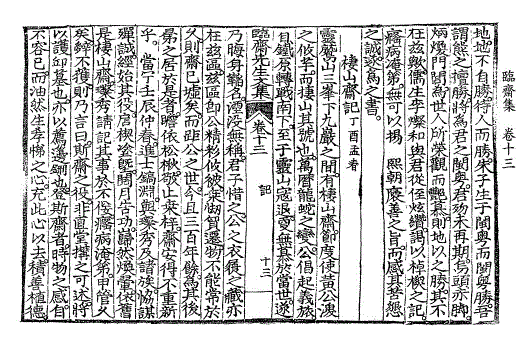 地。地不自胜。待人而胜。朱子生于闽粤而闽粤胜。吾谓熊之擅胜。将为君之闽粤。君歾未再期。乌头赤脚。炳焕门闾。为世人所荣观而艳慕。则地以之胜。其不在玆欤。儒生李灿和与君从侄炫缵。谒以棹楔之记。癃病淹笫。无可以扬 熙朝褒善之旨。而感其苦恳之诚。遂为之书。
地。地不自胜。待人而胜。朱子生于闽粤而闽粤胜。吾谓熊之擅胜。将为君之闽粤。君歾未再期。乌头赤脚。炳焕门闾。为世人所荣观而艳慕。则地以之胜。其不在玆欤。儒生李灿和与君从侄炫缵。谒以棹楔之记。癃病淹笫。无可以扬 熙朝褒善之旨。而感其苦恳之诚。遂为之书。栖山斋记(丁酉孟春)
灵鹫山三峰下九岩之间。有栖山斋。节度使黄公溭之攸芋。而栖山其号也。万历龙蛇之变。公倡起义旅。自铁原转战南下。至于灵山寇退。更无慕于当世。遂乃晦身韬名。湮没无称。君子惜之。公之衣履之藏亦在玆区。玆区即公精彩攸被。桑怯贸迁。物不能常于久。则斋已墟矣。而距公之世。今且三百年馀。为其后昆之居于是者。瞻依松楸。敬止桑梓。斋安得不重新乎。 当宁壬辰仲春。进士镐渊。与璨秀及诸族。协谋殚诚。经始其役。扂楔涂塈。阅月告功。岿然焕翚。依旧是栖山斋。璨秀请记其事于不佞。癃病淹笫。甲管久矣。辞不获。则乃言曰。斯斋之役。非直堂搆之可述。将以护邱墓也。亦以荐笾铏也。登斯斋者。时物之感。自不容已。而油然生孝悌之心。充此心以去。积善植德。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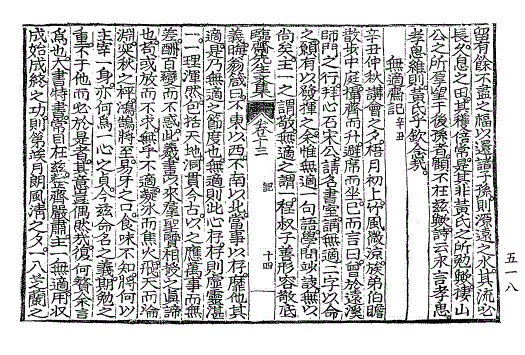 留有馀不尽之福以还诸子孙。则源远之水。其流必长。久息之田。其穫倍常。是其非黄氏之所勉欤。栖山公之所厚望于后孙者。顾不在玆欤。诗云永言孝思。孝思维则。黄氏乎钦念哉。
留有馀不尽之福以还诸子孙。则源远之水。其流必长。久息之田。其穫倍常。是其非黄氏之所勉欤。栖山公之所厚望于后孙者。顾不在玆欤。诗云永言孝思。孝思维则。黄氏乎钦念哉。无适斋记(辛丑)
辛丑仲秋讲会之夕。梧月初上。竹风微凉。族弟伯瞻散步中庭。摄齐而升。避席而坐。已而言曰。曾于远溪师门之行。拜心石宋公。请名书室。诵无适二字以命之。愿有以发挥之。余惟无适一句语。学问妙诀。无以尚矣。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程叔子善形容敬底义。晦翁箴曰。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当事以存。靡他其适。是乃无适之节度也。无适则此心存。存则虚灵湛一。一理浑然。包括天地。洞贯今古。以之应万事而无差。酬百变而不惑。此羲画以来群圣贤相授之真谛也。苟或放而不求。无乎不适。凝冰而焦火。飞天而沦渊。奕秋之枰。鸿鹄将至。易牙之口。食味不知。将何以主宰一身。亦何为一心之贞。今玆命名之义。期勉之重。不于他而必于是者。其意岂偶然哉。复何赘余言为也。大书特书。常目在玆。整齐严肃。主一无适。用收成始成终之功。则第俟月朗风清之夕。一入芝兰之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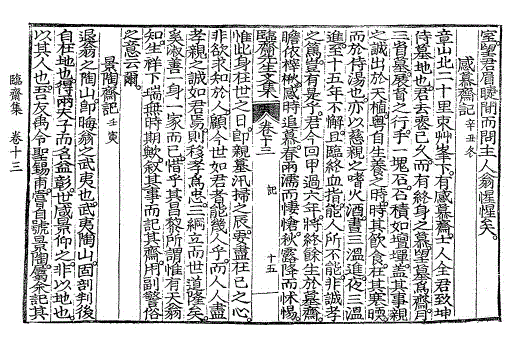 室。望君眉睫间而问主人翁惺惺矣。
室。望君眉睫间而问主人翁惺惺矣。感慕斋记(辛丑冬)
章山北二十里束草峰下。有感慕斋。士人全君致坤侍墓地也。君去丧已久。而有终身之慕。望墓为斋。月三省墓。展省之行。手一块石。石积如坛墠。盖其事亲之诚出于天植。粤自生养之时。时其饮食。在其寒暖。而于侍汤也。亦以慈亲之嗜火酒。昼三温进。夜三温进。至十五年不懈。且临终血指。能人所不能。非诚孝之笃。岂有是乎。君今回甲过六年。将终馀生于墓斋。瞻依梓楸。感时追慕。春雨濡而悽怆。秋露降而怵惕。惟此身在世之日。即亲墓汛扫之辰。要尽在己之心。非欲求知于人。顾今世如君者能几人乎。而人人尽孝亲之诚如君焉。则移孝为忠。三纲立而世道隆矣。奚淑善一身一家而已。惜乎其昌黎所谓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时期欤。叙其事而记其斋。用副警俗之意云尔。
景陶斋记(壬寅)
退翁之陶山。即晦翁之武夷也。武夷陶山。固剖判后自在地也。得两夫子而名益彰。世咸景仰之。非以地也。以其人也。吾友禹令圣锡甫。尝自号景陶。属余记其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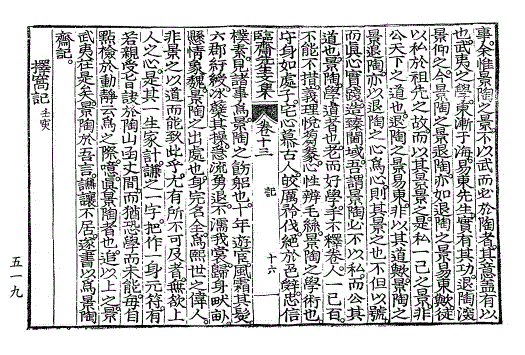 事。余惟景陶之景。不以武而必于陶者。其意盖有以也。武夷之学。东渐于海。易东先生。实有其功。退陶深景仰之。今景陶之景退陶。亦如退陶之景易东欤。徒以私于祖先之故。而以其景景之。是私一己之景。非公天下之道也。退陶之景易东。非以其道欤。景陶之景退陶。亦以退陶之心为心。则其景之也不但以号。而真心实践。造臻阃域。吾谓景陶必不以私。而公其道也。景陶。学道者也。老而好学。手不释卷。人一己百。不能不措。义理悦刍豢。心性辨毛丝。景陶之学术也。守身如处子。宅心慕古人。皎厉矜伐。绝于色辞。忠信朴素。见诸事为。景陶之饬躬也。十年游宦。风霜其发。六郡纡绶。冰檗其操。急流勇退。不濡我裳。归身畎亩。悬情象魏。景陶之出处也。身完名全。为熙世之伟人。非景之以道而能致此乎。尤有所不可及者。无欲上人之心。是其一生家计。谦之一字。把作一身元符。有若亲受旨诀于陶山函丈间。而犹恐学而未能。每自点检于动静云为之际。噫。真景陶者也。追以上之。景武夷在是矣。景陶于吾言。谦让不居。遂书以为景陶斋记。
事。余惟景陶之景。不以武而必于陶者。其意盖有以也。武夷之学。东渐于海。易东先生。实有其功。退陶深景仰之。今景陶之景退陶。亦如退陶之景易东欤。徒以私于祖先之故。而以其景景之。是私一己之景。非公天下之道也。退陶之景易东。非以其道欤。景陶之景退陶。亦以退陶之心为心。则其景之也不但以号。而真心实践。造臻阃域。吾谓景陶必不以私。而公其道也。景陶。学道者也。老而好学。手不释卷。人一己百。不能不措。义理悦刍豢。心性辨毛丝。景陶之学术也。守身如处子。宅心慕古人。皎厉矜伐。绝于色辞。忠信朴素。见诸事为。景陶之饬躬也。十年游宦。风霜其发。六郡纡绶。冰檗其操。急流勇退。不濡我裳。归身畎亩。悬情象魏。景陶之出处也。身完名全。为熙世之伟人。非景之以道而能致此乎。尤有所不可及者。无欲上人之心。是其一生家计。谦之一字。把作一身元符。有若亲受旨诀于陶山函丈间。而犹恐学而未能。每自点检于动静云为之际。噫。真景陶者也。追以上之。景武夷在是矣。景陶于吾言。谦让不居。遂书以为景陶斋记。择窝记(壬寅)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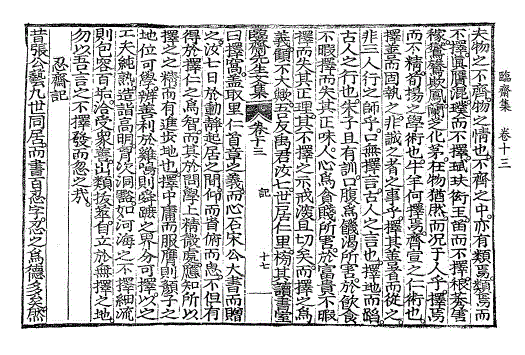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齐之中。亦有类焉。类焉而不择。真赝混。璞而不择。珷玞衒玉。苗而不择。稂莠害稼。鸑鷟欺凤。兰芝化茅。在物犹然。而况于人乎。择焉而不精。荀扬之学术也。牛羊何择焉。齐宣之仁术也。择善而固执之。非诚之者之事乎。择其善者而从之。非三人行之师乎。口无择言。古人之言也。择地而蹈。古人之行也。朱子且有训。口腹为饥渴所害。于饮食不暇择而失其正味。人心为贫贱所害。于富贵不暇择而失其正理。其不择之示戒深且切矣。而择之为义。顾不大欤。吾友禹君汝七。世居仁里。榜其读书室曰择窝。盖取里仁首章之义。而心石宋公大书而赠之。汝七日于动静起居之间。仰而省俯而思。不但有得于择仁之为智。而其于问学上精微处。应知所以择之之精而有进步地也。择中庸而服膺则颜子之地位可学。辨善利于鸡鸣则舜蹠之界分可择。以之工夫纯熟。造诣高明。胸次洞豁。如河海之不择细流则包容百垢。洽受众善。出类拔萃。自立于无择之地。勿以吾言之不择发而忽之哉。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齐之中。亦有类焉。类焉而不择。真赝混。璞而不择。珷玞衒玉。苗而不择。稂莠害稼。鸑鷟欺凤。兰芝化茅。在物犹然。而况于人乎。择焉而不精。荀扬之学术也。牛羊何择焉。齐宣之仁术也。择善而固执之。非诚之者之事乎。择其善者而从之。非三人行之师乎。口无择言。古人之言也。择地而蹈。古人之行也。朱子且有训。口腹为饥渴所害。于饮食不暇择而失其正味。人心为贫贱所害。于富贵不暇择而失其正理。其不择之示戒深且切矣。而择之为义。顾不大欤。吾友禹君汝七。世居仁里。榜其读书室曰择窝。盖取里仁首章之义。而心石宋公大书而赠之。汝七日于动静起居之间。仰而省俯而思。不但有得于择仁之为智。而其于问学上精微处。应知所以择之之精而有进步地也。择中庸而服膺则颜子之地位可学。辨善利于鸡鸣则舜蹠之界分可择。以之工夫纯熟。造诣高明。胸次洞豁。如河海之不择细流则包容百垢。洽受众善。出类拔萃。自立于无择之地。勿以吾言之不择发而忽之哉。忍斋记
昔张公艺九世同居。而书百忍字。忍之为德多矣。然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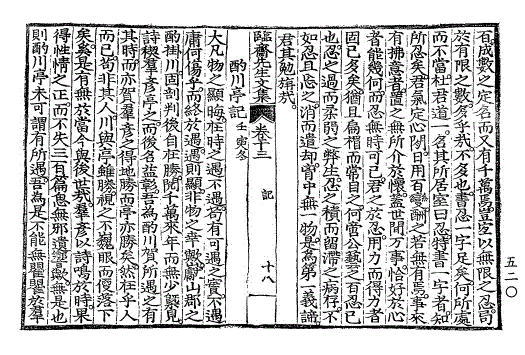 百。成数之定名而又有千万焉。岂宜以无限之忍。局于有限之数。多乎哉。不多也。书忍一字足矣。何所处而不当。杜君道一。名其所居室曰忍。特书一字者。知所忍矣。君气定心閒。日用百变。酬之若无有焉。事来有拂意者。置之无所介于怀。盖世间万事。恰好于心者能几何。而忍无时可已。君之于忍。用力而得力者固已多矣。犹且扁楣而常目之。何啻公艺之百忍已也。忍之过而柔弱之弊生。忍之积而留滞之病存。不如忍且忘之。消而遣却。胸中无一物。是为第一义谛。君其勉旃哉。
百。成数之定名而又有千万焉。岂宜以无限之忍。局于有限之数。多乎哉。不多也。书忍一字足矣。何所处而不当。杜君道一。名其所居室曰忍。特书一字者。知所忍矣。君气定心閒。日用百变。酬之若无有焉。事来有拂意者。置之无所介于怀。盖世间万事。恰好于心者能几何。而忍无时可已。君之于忍。用力而得力者固已多矣。犹且扁楣而常目之。何啻公艺之百忍已也。忍之过而柔弱之弊生。忍之积而留滞之病存。不如忍且忘之。消而遣却。胸中无一物。是为第一义谛。君其勉旃哉。酌川亭记(壬寅冬)
大凡物之显晦。在时之遇不遇。苟有可遇之实。不遇庸何伤乎。而终于遇。遇则显。非物之幸欤。巘山郡之酌挂川。固剖判后自在胜。阅千万来年而无少槩见。诗稧群彦亭之。而后名益彰。吾为酌川贺所遇之有其时。而亦贺群彦之得地胜而亭亦胜矣。然在乎人而已。苟非其人。川与亭虽胜。视之不巍眼而便落下矣。奚是有无于当今与后世哉。群彦以诗鸣于时。果得性情之正。而不失三百篇思无邪遗响欤。无是也则酌川亭未可谓有所遇。吾为是不能无瞿瞿于群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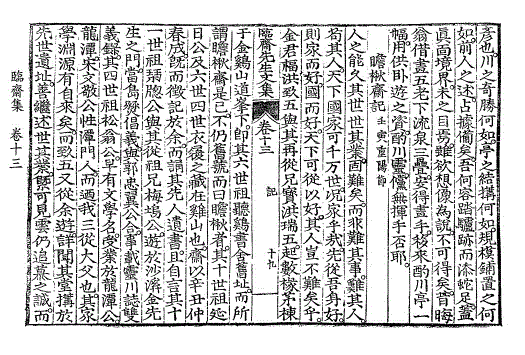 彦也。川之奇胜何如。亭之结搆何如。规模铺置之何如。前人之述。占据备矣。吾何容踏驴迹而添蛇足。盖真面境界。未之目焉。虽欲想像为说。不可得矣。昔晦翁借画五老下流泉三叠。安得画手。移来酌川亭一幅。用供卧游之资。酌川灵。傥无挥手否耶。
彦也。川之奇胜何如。亭之结搆何如。规模铺置之何如。前人之述。占据备矣。吾何容踏驴迹而添蛇足。盖真面境界。未之目焉。虽欲想像为说。不可得矣。昔晦翁借画五老下流泉三叠。安得画手。移来酌川亭一幅。用供卧游之资。酌川灵。傥无挥手否耶。瞻楸斋记(壬寅重阳节)
人之能久其世世其业。固难矣。而非难其事。难其人。苟其人。天下国家可千万世。况家乎哉。先从吾身好。则家而好。国而好。天下可从以好。其人岂不难矣乎。金君福洪致五与其再从兄宝洪瑞五。起数椽茅栋于金鸡山道峰下。即其六世祖听鸡书舍旧址。而所谓瞻楸斋是已。不仍旧号而曰瞻楸者。其十世祖延日公及六世四世衣履之藏在鸡山也。斋以辛丑仲春成。既而徵记于余。而诵其先人遗书。且自言其十一世祖琴窗公与其从祖兄梅坞公。游于沙溪金先生之门。当岛燹倡义。与郭忠翼公合。事载灵川志双义录。其四世祖松翁公。早有文学名。受业于龙潭公。龙潭。宋文敬公性潭门人。而乃我三从大父也。其家学渊源有自来矣。而致五又从余游。详闻其堂搆于先世遗址。善继述世其业。槩可见云仍追慕之诚。而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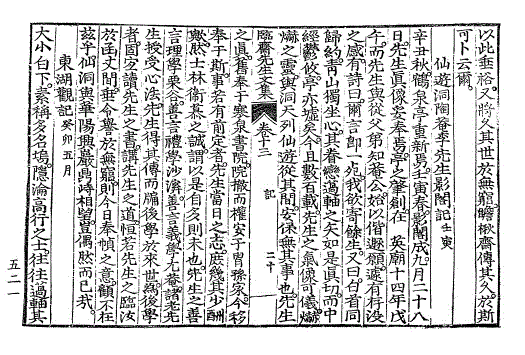 以此垂裕。又将久其世于无穷。瞻楸斋传其久。于斯可卜云尔。
以此垂裕。又将久其世于无穷。瞻楸斋传其久。于斯可卜云尔。仙游洞陶庵李先生影阁记(壬寅)
辛丑秋。鹤泉亭重新焉。壬寅春。影阁成。九月二十八日。先生真像妥奉焉。亭之肇创。在 英庙十四年戊午。而先生与从父弟知庵公。始以偕遁愿。遽有存没之感。有诗曰。尔言即一死。我欲寄馀生。又曰。白首同归约。青山独坐心。其眷恋薖轴之矢如是真切。而中经郁攸。亭亦墟矣。今且数百载。先生之气像可仪。赫赫之灵。与洞天列仙游从其间。安保无其事也。先生之真。旧奉于寒泉书院。院撤而权安于胄孙家。今移奉于斯。事若有前定者。先生当日之志。庶几其少酬欤。然士林卫慕之诚。谓以是自多则未也。先生之善言理学栗谷。善言礼学沙溪。善言义学尤庵。诸老先生授受心法。先生得其传而牖后学于来世。为后学者。固宜读先生之书。讲先生之道。恒若先生之临汝于函丈间。垂令誉于无穷。则今日奉帧之意。顾不在玆乎。仙洞与华阳兴岩鼎峙相望。岂偶然而已哉。
东湖观记(癸卯五月)
大小白下。素称多名坞。隐沦高行之士。往往薖轴其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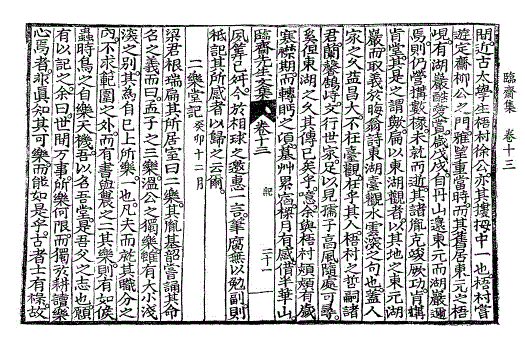 间。近古太学生梧村徐公。亦其搂拇中一也。梧村尝游定斋柳公之门。雅望重当时。而其旧居东元之梧岘。有湖岩酷爱赏。岁戊戌。自丹山还东元而湖岩迩焉。则仍营搆数椽。未就而逝。其诸胤克竣厥功。肯搆肯堂。其是之谓欤。扁以东湖观者。以其地之东元湖岩。而取义于晦翁诗东湖台观水云深之句也。盖人家之久益昌大。不在台观。在乎其人。梧村之哲嗣诸君。兰馨鹄峙。文行世家。足以见孺子高风随处可寻。奚但东湖之久其传已矣乎。噫。余与梧村颎颎有岁寒襟期。而转眄之顷。墓草累宿。梁月有感。借半华山。夙算已舛。今于相球之邀惠一言。笔腐无以勉副。则秪记其所感者以归之云尔。
间。近古太学生梧村徐公。亦其搂拇中一也。梧村尝游定斋柳公之门。雅望重当时。而其旧居东元之梧岘。有湖岩酷爱赏。岁戊戌。自丹山还东元而湖岩迩焉。则仍营搆数椽。未就而逝。其诸胤克竣厥功。肯搆肯堂。其是之谓欤。扁以东湖观者。以其地之东元湖岩。而取义于晦翁诗东湖台观水云深之句也。盖人家之久益昌大。不在台观。在乎其人。梧村之哲嗣诸君。兰馨鹄峙。文行世家。足以见孺子高风随处可寻。奚但东湖之久其传已矣乎。噫。余与梧村颎颎有岁寒襟期。而转眄之顷。墓草累宿。梁月有感。借半华山。夙算已舛。今于相球之邀惠一言。笔腐无以勉副。则秪记其所感者以归之云尔。二乐堂记(癸卯十二月)
梁君根瑞扁其所居室曰二乐。其胤基韶尝诵其命名之义而曰。孟子之三乐。温公之独乐。虽有大小浅深之别。其为自己上所乐。一也。凡夫而就其职分之内。不求范围之外。而有书与农之二其乐。则有如候虫时鸟之自乐天机。吾以名吾堂。是吾父之志也。愿有以记之。余曰。世间万事。所乐何限。而独于耕读乐心焉者。非真知其可乐。而能如是乎。古者士有禄。故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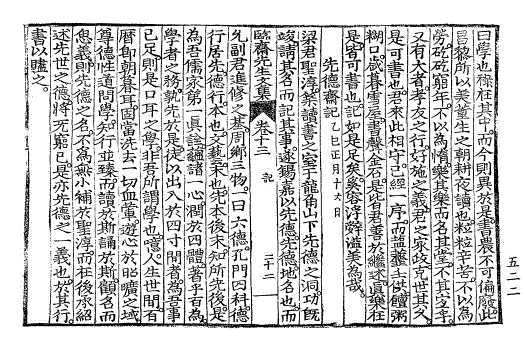 曰学也禄在其中。而今则异于是。书农不可偏废。此昌黎所以美董生之朝耕夜读也。粒粒辛苦。不以为劳。矻矻穷年。不以为惰。乐其乐而名其堂。不其宜乎。又有大者。孝友之行。好施之义。君之家政。克世其久。是可书也。君来此相守。已经一序。而盐齑壬供。饘粥糊口。岁暮雪屋。书声金石。是皆君善于继述。真乐在是。皆可书也。记如是足矣。奚容浮辞溢美为哉。
曰学也禄在其中。而今则异于是。书农不可偏废。此昌黎所以美董生之朝耕夜读也。粒粒辛苦。不以为劳。矻矻穷年。不以为惰。乐其乐而名其堂。不其宜乎。又有大者。孝友之行。好施之义。君之家政。克世其久。是可书也。君来此相守。已经一序。而盐齑壬供。饘粥糊口。岁暮雪屋。书声金石。是皆君善于继述。真乐在是。皆可书也。记如是足矣。奚容浮辞溢美为哉。先德斋记(乙巳正月十六日)
梁君圣淳。筑读书之室于龙角山下先德之洞。功既竣。请其名而记其事。遂锡嘉以先德。先德。地名也。而允副君进修之基。周乡三物。一曰六德。孔门四科。德行居先。德行。本也。文艺。末也。先本后末。知所先后。是为吾儒家第一真诠。蕴诸一心。润于四体。著乎百为。学者之务。孰先于是。徒以出入于四寸间者。为吾事已足。则是口耳之学。非吾所谓学也。噫。人生世间。百历即朝暮耳。固当洗去一切血荤。游心于昭旷之域。尊德性道问学。知行并臻。而读于斯诵于斯。顾名而思义。则先德之名。不为无小补于圣淳。而在后承绍述先世之德。将无穷已。是亦先德之一义也。于其行。书以赆之。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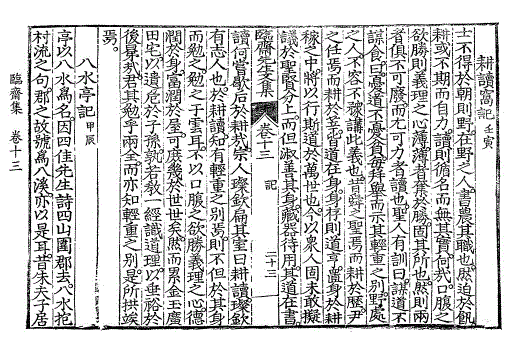 耕读窝记(壬寅)
耕读窝记(壬寅)士不得于朝则野。在野之人。书农其职也。然迫于饥。耕或不期而自力。读则循名而无其实。何哉。口腹之欲胜则义理之心薄。薄者夺于胜。固其所也。然则两者俱不可废。而尤可力者读也。圣人有训曰。谋道不谋食。曰。忧道不忧贫。每并举而示其轻重之别。野处之人。不容不豫讲此义也。昔舜之圣焉而耕于历。尹之任焉而耕于莘。皆道在身。身存则道亨。置身于耕稼之中。将以行斯道于万世也。今以众人固未敢拟议于圣贤分上。而但淑善其身。藏器待用。其道在书。读何尝歇后于耕哉。宗人璨钦扁其室曰耕读。璨钦有志人也。于耕读。知有轻重之别焉。则不但于其身而勉之。勉之于云耳。不以口腹之欲胜义理之心。德润于身。富润于屋。可庶几于世世矣。然而累金玉广田宅。以遗危于子孙。孰若教一经识道理。以垂裕于后昆哉。君其勉乎两全。而亦知轻重之别。是所拱俟焉。
八水亭记(甲辰)
亭以八水为名。因四佳先生诗四山围郡去。八水抱村流之句。郡之故号为八溪。亦以是耳。昔朱夫子居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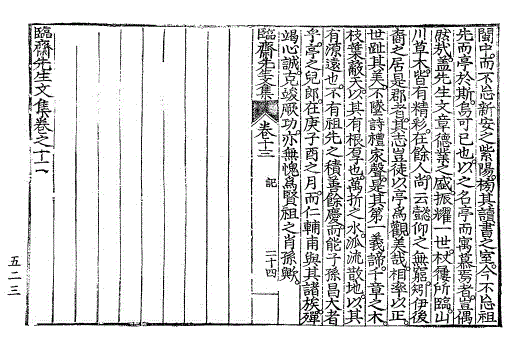 闽中。而不忘新安之紫阳。榜其读书之室。今不忘祖先而亭于斯。乌可已也。以之名亭而寓慕焉者。岂偶然哉。盖先生文章德业之盛。振耀一世。杖屦所临。山川草木。皆有精彩。在馀人。尚云懿仰之无穷。矧伊后裔之居是郡者。其志岂徒以亭为观美哉。相率以正。世趾其美。不坠诗礼家声。是其第一义谛。千章之木。枝叶蔽天。以其有根厚也。万折之水。派流散地。以其有源远也。不有祖先之积善馀庆。而能子孙昌大者乎。亭之儿郎。在庚子酉之月。而仁辅甫与其诸族。殚竭心诚。克竣厥功。亦无愧为贤祖之肖孙欤。
闽中。而不忘新安之紫阳。榜其读书之室。今不忘祖先而亭于斯。乌可已也。以之名亭而寓慕焉者。岂偶然哉。盖先生文章德业之盛。振耀一世。杖屦所临。山川草木。皆有精彩。在馀人。尚云懿仰之无穷。矧伊后裔之居是郡者。其志岂徒以亭为观美哉。相率以正。世趾其美。不坠诗礼家声。是其第一义谛。千章之木。枝叶蔽天。以其有根厚也。万折之水。派流散地。以其有源远也。不有祖先之积善馀庆。而能子孙昌大者乎。亭之儿郎。在庚子酉之月。而仁辅甫与其诸族。殚竭心诚。克竣厥功。亦无愧为贤祖之肖孙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