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杂著
杂著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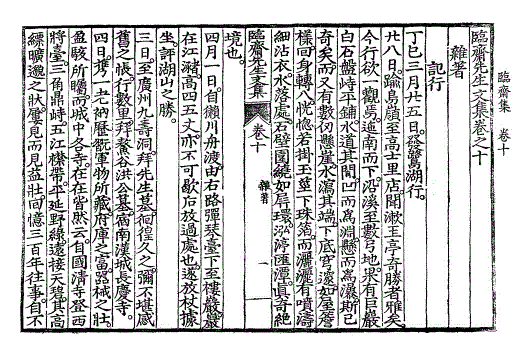 记行
记行丁巳三月廿五日。发鹭湖行。
廿八日。踰鸟岭至高士里店。闻漱玉亭奇胜者雅矣。今行欲一观焉。迤南而下。沿溪至数弓地。果有巨岩白石盘峙平铺。水道其间。凹而为渊。悬而为瀑。斯已奇矣。而又有数仞悬崖。水泻其端。下底穹邃。如屋檐样。回身转入。恍惚若挂玉茎下珠箔。而洒洒有喷涛细沾衣。水落处。石壁围绕如屏环。泓渟汇潭。真奇绝境也。
四月一日。自獭川舟渡。由右路弹琴台下至楼岩。岩在江潴。高四五丈。亦不可歇后放过处也。遂放杖据坐。评湖山之胜。
三日。至广州九寿洞。拜先生墓。徊徨久之。弥不堪感旧之怅。行数里。拜鳌谷洪公墓。宿南汉城长庆寺。
四日。携一老衲历玩军物所藏。府库之富。器械之壮。盈骇所瞩。而城中各寺。在在皆然云。自国清寺登西将台。三角鼎峙。五江襟带。平延野绿。远接天碧。其高缥旷邈之状。屡见而见益壮。回忆三百年往事。自不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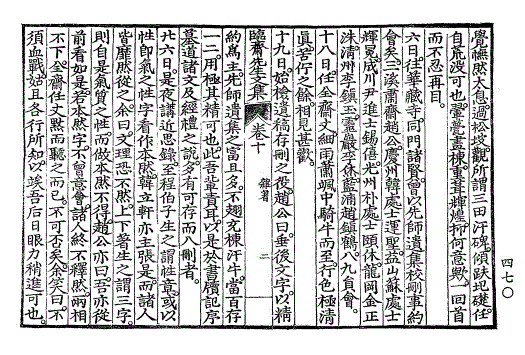 觉怃然太息。过松坡。观所谓三田汗碑。倾趺圮础。任自荒没可也。翚甍画栋。重葺辉煌。抑何意欤。一回首而不忍再目。
觉怃然太息。过松坡。观所谓三田汗碑。倾趺圮础。任自荒没可也。翚甍画栋。重葺辉煌。抑何意欤。一回首而不忍再目。六日。往华藏寺。同门诸贤。曾以先师遗集校删事约会矣。三溪肃斋赵公。庆州韩处士运圣。益山苏处士辉冕。成川尹进士锡僖。光州朴处士颐休。龙冈金正洙。清州李镇玉。灵岩李炰。蓝浦赵镇鹤。八九员会。
十八日。任全斋丈。细雨萧飒中骑牛而至。行色极清真。苦伫之馀。相见甚欢。
十九日。始检遗稿存删之役。赵公曰。垂后文字。以精约为主。先师遗集之富且多。不翅充栋汗牛。当百存一二。用极其精可也。此吾辈责耳。以是于书牍记序墓道诸文及经礼之说。多有可存而入删者。
廿六日。是夜讲近思录。至程伯子生之谓性章。或以性即气之性字看作本然。韩立轩亦主张是。而诸人皆靡然从之。余曰。文理恐不然。上下著生之谓三字。则自是气质之性。而做本然不得。赵公亦曰。吾亦从前看如是。若本然字。不曾意会。诸人终不释然。两相不下。全斋任丈默而听之而已。不可否矣。余笑曰。不须血战。姑且各行所知。以俟吾后日眼力稍进可也。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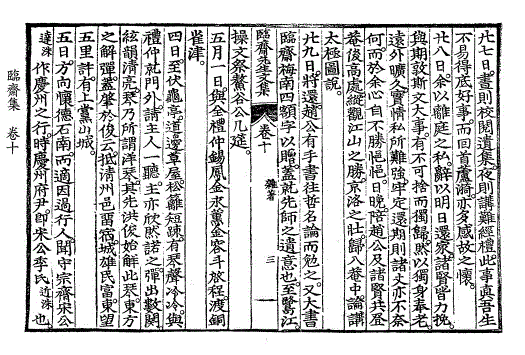 廿七日。昼则校阅遗集。夜则讲难经礼。此事真吾生不易得底好事。而回首芦漪。亦多感故之怀。
廿七日。昼则校阅遗集。夜则讲难经礼。此事真吾生不易得底好事。而回首芦漪。亦多感故之怀。廿八日。余以离庭之私。辞以明日还家。诸贤皆力挽。与期敦斯文大事。有不可舍而独归。然以独身奉老。远外旷久。实情私所难强。牢定还期则诸丈亦不奈何。而于余心自不胜悒悒。日晚。陪赵公及诸贤共登庵后高处。纵观江山之胜。京洛之壮。归入庵中。论讲太极图说。
廿九日。将还。赵公有手书往哲名论而勉之。又大书临斋梅南四额字以赠。盖就先师之遗意也。至鹭江。操文祭鳌谷公几筵。
五月一日。与全礼仲锡凤,金永薰,金容斗启程。渡铜雀津。
四日。至伏龟亭。道边草屋。松篱短疏。有琴声冷冷。与礼仲就门外。请主人一听。主亦欣然诺之。弹出数阕。弦韵清亮。琴乃所谓洋琴。其先洪俊始解此琴。东方之解弹。盖肇于俊云。抵清州邑留宿。城雄民富。东望五里许。有上党山城。
五日。方向怀德石南。而适因过行人。闻守宗斋宋公(达洙)作庆州之行。时庆州府尹。即宋公季氏(近洙)也。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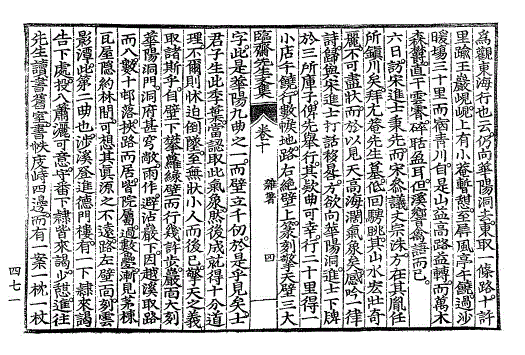 为观东海行也云。仍向华阳洞去。东取一条路。十许里踰王岩岘。岘上有小庵暂憩。至屏风亭午饶。过沙暖场三十里而宿青川。自是山益高路益转。而万木森郁。直干云霄。碎聒盈耳。但溪响禽语而已。
为观东海行也云。仍向华阳洞去。东取一条路。十许里踰王岩岘。岘上有小庵暂憩。至屏风亭午饶。过沙暖场三十里而宿青川。自是山益高路益转。而万木森郁。直干云霄。碎聒盈耳。但溪响禽语而已。六日。访宋进士秉先。而宋参议丈宗洙。方在其胤任所镇川矣。拜尤庵先生墓。低回骋眺。其山水宏壮奇丽。不可尽状。而于以见天高海阔气象矣。感吟一律诗。归与宋进士打话移晷。方欲向华阳洞。进士下牌于三所库子。俾先举行。其款曲可幸。行二十里得一小店午饶。行数帿地。路右绝壁上。篆刻擎天壁三大字。此是华阳九曲之一。而壁立千仞。于是乎见矣。士君子生此季叶。当认取此气象。然后成就得十分道理。不尔则怵迫倒坠。至无状小人而后已。擎天之义。取诸斯乎。自壁下攀萝缘壁而行几许步。岩面大刻华阳洞门。洞府甚穹敞。雨作。避沾岩下。因越溪取路而入。数十村落。挟路而居。皆院属。过数叠。渐见茅栋瓦屋隐约林间。可想其真源之不远。路左壁面。刻云影潭。此第二曲也。涉溪登进德门楼。有一下隶来谒告下处。投入萧洒可意。守番下隶皆来谒。少憩。进往先生读书旧室。书帙庋峙四边。而有一案一枕一杖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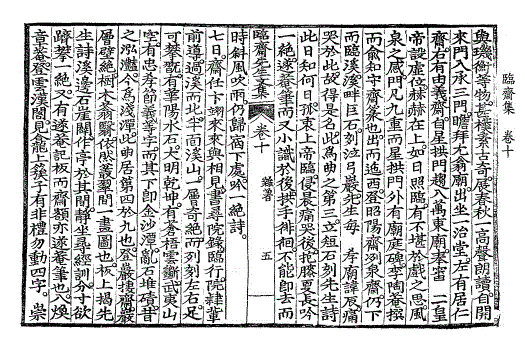 与玑衡等物。甚朴素古奇。展春秋一高声朗读。自开来门入承三门。瞻拜尤翁庙。出坐一治堂。左有居仁斋。右有由义斋。自星拱门趋入万东庙。奉审 二皇帝设虚位。赫赫在上。如日照临。有不堪于戏之思。风泉之感。门凡九重而星拱门外有庙庭碑。李陶庵撰而俞知守斋篆也。出而迤西。登昭阳斋冽泉斋。仍下而临溪。溪畔巨石。刻泣弓岩。先生每 孝庙讳辰。痛哭于此。故得是名。此为曲之第三。立短石刻先生诗此日知何日。孤衷上帝临。侵晨痛哭后。抱膝更长吟一绝。遂庵笔而又小识于后。拱手徘徊。不能即去而时斜风吹雨。仍归宿下处。吟一绝诗。
与玑衡等物。甚朴素古奇。展春秋一高声朗读。自开来门入承三门。瞻拜尤翁庙。出坐一治堂。左有居仁斋。右有由义斋。自星拱门趋入万东庙。奉审 二皇帝设虚位。赫赫在上。如日照临。有不堪于戏之思。风泉之感。门凡九重而星拱门外有庙庭碑。李陶庵撰而俞知守斋篆也。出而迤西。登昭阳斋冽泉斋。仍下而临溪。溪畔巨石。刻泣弓岩。先生每 孝庙讳辰。痛哭于此。故得是名。此为曲之第三。立短石刻先生诗此日知何日。孤衷上帝临。侵晨痛哭后。抱膝更长吟一绝。遂庵笔而又小识于后。拱手徘徊。不能即去而时斜风吹雨。仍归宿下处。吟一绝诗。七日。斋任卞翊来来与相见。书寻院录。临行。院隶辈前导。过溪而北。半面溪山。一层奇绝。而列刻左右。足可攀玩。有华阳水石。大明乾坤。有苍梧云断。武夷山空。有忠孝节义等字。而其下即金沙潭。乱石堆碛。昔之泓滟。今为浅潬。此曲居第四于九也。登岩栖斋。岩层壁绝。树木蓊翳。依然丛翠间一画图也。板上揭先生诗溪边石崖辟。作亭于其间。静坐寻经训。分寸欲跻攀一绝。又有遂庵记板而斋额亦遂庵笔也。入焕章庵。登云汉阁。见龛上簇子有非礼勿动四字。 崇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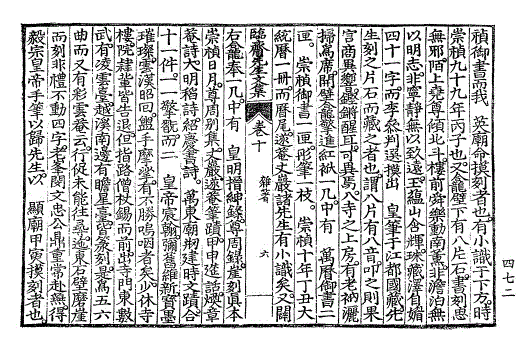 祯御书而我 英庙命摸刻者也。有小识于下方。时崇祯九十九年丙子也。又龛壁下有八片石。书刻思无邪。陌上尧尊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玉蕴山含辉。珠藏泽自媚四十一字。而李参判选摸出 皇笔于江都国藏。先生刻之片石而藏之者也。谓八片有八音。叩之则果宫商异响。铿锵醒耳。可异焉。入寺之上房。有老衲洒扫为席。开壁龛擎进红袱一几。中有 万历御书二匣。 崇祯御书一匣。彤笔一枝。 崇祯十年丁丑大统历一册。而历尾。遂庵丈岩诸先生有小识矣。又辟右龛奉一几。中有 皇明搢绅录。尊周录。崖刻真本崇祯日月。尊周别集。丈岩,遂庵笔迹。甲申筵话。焕章庵诗。大明稻诗。绍庆书诗。 万东庙刱建时文迹。合十一件。一一擎玩。而二 皇帝宸翰。弥旧维新。宝墨璀璨。云汉昭回。盥手摩挲。有不胜呜咽者矣。少休寺楼。院隶辈皆告退。但指路僧杖锡而前。出寺门东数武。有凌云台。越溪南边有瞻星台。皆篆刻。是为五六曲而又有彩云庵云。行促未能往寻。迤东石壁磨崖而刻非礼不动四字。老峰闵文忠公鼎重常赴燕。得毅宗皇帝手笔以归先生。以 显庙甲寅摸刻者也。
祯御书而我 英庙命摸刻者也。有小识于下方。时崇祯九十九年丙子也。又龛壁下有八片石。书刻思无邪。陌上尧尊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玉蕴山含辉。珠藏泽自媚四十一字。而李参判选摸出 皇笔于江都国藏。先生刻之片石而藏之者也。谓八片有八音。叩之则果宫商异响。铿锵醒耳。可异焉。入寺之上房。有老衲洒扫为席。开壁龛擎进红袱一几。中有 万历御书二匣。 崇祯御书一匣。彤笔一枝。 崇祯十年丁丑大统历一册。而历尾。遂庵丈岩诸先生有小识矣。又辟右龛奉一几。中有 皇明搢绅录。尊周录。崖刻真本崇祯日月。尊周别集。丈岩,遂庵笔迹。甲申筵话。焕章庵诗。大明稻诗。绍庆书诗。 万东庙刱建时文迹。合十一件。一一擎玩。而二 皇帝宸翰。弥旧维新。宝墨璀璨。云汉昭回。盥手摩挲。有不胜呜咽者矣。少休寺楼。院隶辈皆告退。但指路僧杖锡而前。出寺门东数武。有凌云台。越溪南边有瞻星台。皆篆刻。是为五六曲而又有彩云庵云。行促未能往寻。迤东石壁磨崖而刻非礼不动四字。老峰闵文忠公鼎重常赴燕。得毅宗皇帝手笔以归先生。以 显庙甲寅摸刻者也。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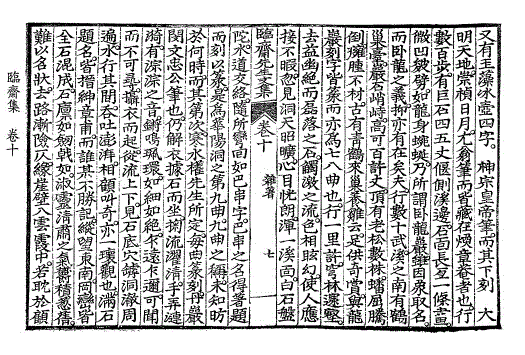 又有玉藻冰壶四字。 神宗皇帝笔。而其下刻 大明天地。崇祯日月。尤翁笔而皆藏在焕章庵者也。行数百步。有巨石四五丈偃侧溪边。石面长亘一条画。微凹皴劈。如龙身蜿蜒。乃所谓卧龙岩。虽因象取名。而卧龙之义。抑亦有在矣夫。行数十武。溪之南有鹤巢台。岩石峭峙。高可百许丈。顶有老松数株。蟠屈腾倒。痈肿不材。古有青鹤来巢养雏云。足供奇赏。与龙岩刻字皆篆而亦为七八曲也。行一里许。穹林邃壑。去益幽绝而磊落之石。触激之流。色相眩幻。使人应接不暇。忽见洞天昭旷。心目恍朗。浑一溪面。白石盘陀。水道交络。随所弯回如巴串字。巴串之名得著题而刻以篆。是为华阳洞之第九曲。九曲之称。未知昉于何时。而其第次。寒水权先生所定。每曲篆刻。丹岩闵文忠公笔也。仍解衣据石而坐。掬流濯清。手弄涟漪。有淙淙之音。锵鸣佩环。如细如绝。乍远乍迩。可闻而不可寻。摄衣而起。从流上下。见石底穴罅洞澈周遍。水行其间。吞吐澎湃。相顾叫奇。亦一瑰观也。满石题名。皆搢绅章甫。而谁某不胜记。纵望东南。冈峦皆全石混成。石廪如剑戟如。淑灵清肃之气郁积葱茜。难以名状。去路渐险仄。缘崖壁入云霞中。若耽于顾
又有玉藻冰壶四字。 神宗皇帝笔。而其下刻 大明天地。崇祯日月。尤翁笔而皆藏在焕章庵者也。行数百步。有巨石四五丈偃侧溪边。石面长亘一条画。微凹皴劈。如龙身蜿蜒。乃所谓卧龙岩。虽因象取名。而卧龙之义。抑亦有在矣夫。行数十武。溪之南有鹤巢台。岩石峭峙。高可百许丈。顶有老松数株。蟠屈腾倒。痈肿不材。古有青鹤来巢养雏云。足供奇赏。与龙岩刻字皆篆而亦为七八曲也。行一里许。穹林邃壑。去益幽绝而磊落之石。触激之流。色相眩幻。使人应接不暇。忽见洞天昭旷。心目恍朗。浑一溪面。白石盘陀。水道交络。随所弯回如巴串字。巴串之名得著题而刻以篆。是为华阳洞之第九曲。九曲之称。未知昉于何时。而其第次。寒水权先生所定。每曲篆刻。丹岩闵文忠公笔也。仍解衣据石而坐。掬流濯清。手弄涟漪。有淙淙之音。锵鸣佩环。如细如绝。乍远乍迩。可闻而不可寻。摄衣而起。从流上下。见石底穴罅洞澈周遍。水行其间。吞吐澎湃。相顾叫奇。亦一瑰观也。满石题名。皆搢绅章甫。而谁某不胜记。纵望东南。冈峦皆全石混成。石廪如剑戟如。淑灵清肃之气郁积葱茜。难以名状。去路渐险仄。缘崖壁入云霞中。若耽于顾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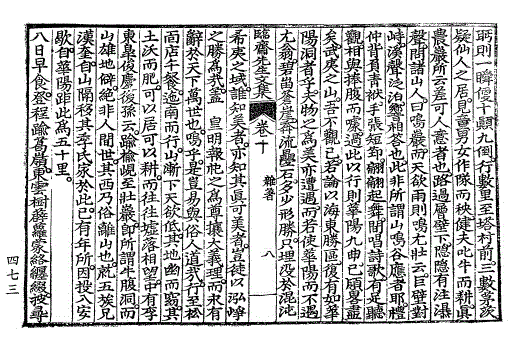 眄则一瞬便十颠九倒。行数里至塔村前。三数茅茨。疑仙人之居。见童男女作队而秧。健夫叱牛而耕。真农岩所云差可人意者也。路过层壁下。隐隐有注瀑声。问诸山人。曰鸣岩。而天欲雨则鸣尤壮云。巨壁对峙。溪声泛泊。响相答也。此非所谓山鸣谷应者耶。礼仲背负青袱。手张短筇。翩翩起舞。间唱诗歌。有足听观。相与捧腹而噱。过此以行则华阳九曲。已领略尽矣。武夷之山。吾不观已。若论以海东胜区。复有如华阳洞者乎。夫物之为美亦遭遇。而若使华阳而不遇尤翁。碧岫苍崖。奔流叠石。多少形胜。只埋没于混沌希夷之域。谁知美者。亦知其真可美者。岂徒以泓峥之胜为哉。盖 皇明报祀之为尊攘大义理。而永有辞于天下万世也。呜乎。是岂易与俗人道哉。行至松面店午餐。迤南而行。山渐下天欲低。其地幽而窈。其土沃而肥。可以居可以耕。而往往墟落相望。中有李东皋俊庆后孙云。踰榆岘至壮岩。即所谓牛腹洞。而山雄地僻。绝非人间世。其西乃俗离山也。就五族兄汉奎。自山隔移其季氏家于此。已有年所。因投入安歇。自华阳距此为五十里。
眄则一瞬便十颠九倒。行数里至塔村前。三数茅茨。疑仙人之居。见童男女作队而秧。健夫叱牛而耕。真农岩所云差可人意者也。路过层壁下。隐隐有注瀑声。问诸山人。曰鸣岩。而天欲雨则鸣尤壮云。巨壁对峙。溪声泛泊。响相答也。此非所谓山鸣谷应者耶。礼仲背负青袱。手张短筇。翩翩起舞。间唱诗歌。有足听观。相与捧腹而噱。过此以行则华阳九曲。已领略尽矣。武夷之山。吾不观已。若论以海东胜区。复有如华阳洞者乎。夫物之为美亦遭遇。而若使华阳而不遇尤翁。碧岫苍崖。奔流叠石。多少形胜。只埋没于混沌希夷之域。谁知美者。亦知其真可美者。岂徒以泓峥之胜为哉。盖 皇明报祀之为尊攘大义理。而永有辞于天下万世也。呜乎。是岂易与俗人道哉。行至松面店午餐。迤南而行。山渐下天欲低。其地幽而窈。其土沃而肥。可以居可以耕。而往往墟落相望。中有李东皋俊庆后孙云。踰榆岘至壮岩。即所谓牛腹洞。而山雄地僻。绝非人间世。其西乃俗离山也。就五族兄汉奎。自山隔移其季氏家于此。已有年所。因投入安歇。自华阳距此为五十里。八日早食。登程踰葛岭。东云树薜萝蒙络缠缀。披寻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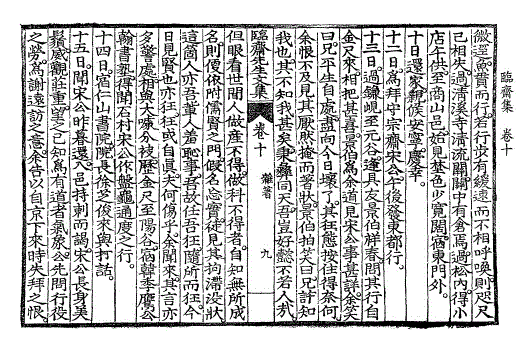 微径。鱼贯而行。若行步有缓速而不相呼唤。则咫尺已相失。过清溪寺清流关。关中有仓焉。过松内。得小店午供。至商山邑。始见野色少宽阔。宿东门外。
微径。鱼贯而行。若行步有缓速而不相呼唤。则咫尺已相失。过清溪寺清流关。关中有仓焉。过松内。得小店午供。至商山邑。始见野色少宽阔。宿东门外。十日还家。亲候安宁。庆幸。
十二日。为拜守宗斋宋公。午后发东都行。
十三日。过镰岘至元谷。逢具友景伯祥春。问其行自金尺来。相把甚喜。景伯为余道见宋公事甚详。余笑曰。兄平生自处。尽向今日坏了。其狂态按住得奈何。余恨不及见其厌然掩而著状。景伯拍笑曰。兄许知我也。其不知我甚矣。秉彝同天。吾岂好懿不若人哉。但眼看世间人做产不得。做科不得者。自知无所成名。则便依附儒贤之门。假名忘实。徒见其拘滞没状。这个人亦吾辈人羞耻事。吾故任吾狂。随所而狂。今日见贤也亦狂。狂或自真。夫何伤乎。余闻来。其言亦多警处。相与大噱分袂。历金尺至阳谷。宿韩季鹰公翰书塾。得闻石村宋公作盘龟通度之行。
十四日。宿仁山书院。院长徐芝俊来与打话。
十五日。闻宋公昨墓还。入邑持刺而谒。宋公长身美须。威观庄重。望之已知为有道者气象。公先问行役之劳。为谢远访之意。余告以自京下来时失拜之恨。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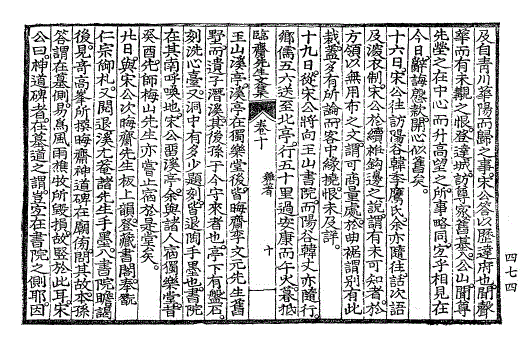 及自青川华阳而归之事。宋公答以历达府也。闻声华而有未觏之恨。登达城。访尊家旧基。入公山。闻尊先茔之在中心而升高望之。所事略同。宜乎相见在今日。辞诲慇款。开心似旧矣。
及自青川华阳而归之事。宋公答以历达府也。闻声华而有未觏之恨。登达城。访尊家旧基。入公山。闻尊先茔之在中心而升高望之。所事略同。宜乎相见在今日。辞诲慇款。开心似旧矣。十六日。宋公往访阳谷韩季鹰氏。余亦随往。话次语及深衣制。宋公于续衽钩边之说。谓有未可知者。于方领以无用布之文。谓可商量处。于曲裾谓别有此裁。盖多有所论。而客中缘挠。恨未及详。
十九日。从宋公将向玉山书院。而阳谷韩丈亦随行。乡儒五六送至北亭。行五十里过安康而午火。暮抵玉山溪亭。溪亭在独乐堂后。皆晦斋李文元先生旧墅。而遗子潜溪。其后孙于今守来者也。亭下有盘石。刻洗心台。又洞中有多少题刻。皆退陶手墨也。书院在其南呼唤地。宋公留溪亭。余与诸人宿独乐堂。昔癸酉。先师梅山先生亦尝止宿于是堂矣。
廿日。与宋公次晦斋先生板上韵。登藏书阁。奉玩 仁宗御札。又阅退溪尤庵诸先生手墨。入书院瞻谒后。见奇高峰所撰晦斋神道碑在庙傍。问其故。本孙答谓在墓侧。易为风雨樵牧所毁损。故竖于此耳。宋公曰。神道碑者。在墓道之谓。岂宜在书院之侧耶。因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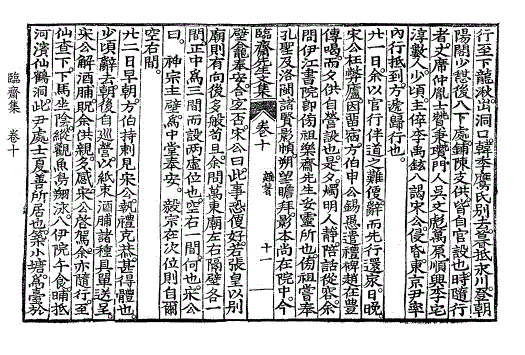 行至下龙湫。出洞口。韩季鹰氏别去。暮抵永川。登朝阳阁少憩后入下处。铺陈支供。皆自官设也。时随行者。丈席仲胤士赞秉瓒,门人吴文彪万原,顺兴李宅淳数人。少顷。主倅李禹铉入谒宋公。侵昏。东京尹率内行抵到。方递归行也。
行至下龙湫。出洞口。韩季鹰氏别去。暮抵永川。登朝阳阁少憩后入下处。铺陈支供。皆自官设也。时随行者。丈席仲胤士赞秉瓒,门人吴文彪万原,顺兴李宅淳数人。少顷。主倅李禹铉入谒宋公。侵昏。东京尹率内行抵到。方递归行也。廿一日。余以官行伴道之难便。辞而先行还家。日晚。宋公枉弊庐。因留宿。方伯申公锡愚遣礼裨赵在礼传喝。而夕供自营设也。是夕。烛明人静。陪话从容。余问伊江书院即傍祖乐斋先生妥灵所也。傍祖尝奉孔圣及洛闽诸贤影帧。朔望瞻拜。影本尚在院中。今壁龛奉安。合宜否。宋公曰。此事恐便好。若张皇以别庙则有向后多般苟且。余问万东庙左右隔壁各一间。正中为三间而设两虚位也。空右一间。何也。宋公曰。 神宗主壁。为中堂奉安。 毅宗在次位则自尔空右间。
廿二日早朝。方伯持刺见宋公。执礼克恭。甚得体也。少顷辞去。朝后自巡营。以纸束酒脯诸种具单送呈。宋公解酒脯。贶余供亲。多感。宋公启驾。余亦随行。至仙查下。下马坐阴。纵观鱼鸟翔泳。入伊院午食。晡抵河滨仙鹤洞。此尹处士夏善所居也。筑小塘。为台于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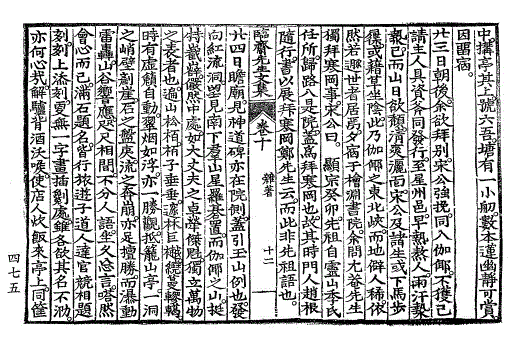 中。搆亭其上。号六吾。塘有一小舠。数本莲幽静可赏。因留宿。
中。搆亭其上。号六吾。塘有一小舠。数本莲幽静可赏。因留宿。廿三日朝后。余欲拜别。宋公强挽。同入伽倻。不获已请主人具资斧同发行。至星州邑。早热熬人。雨汗漐漐。已而山日欲颓。清爽洒面。宋公及诸生或下马步屧。或藉草坐阴。此乃伽倻之东北峡。而地僻人稀。依然若遁世者居焉。夕宿于桧渊书院。余问尤庵先生独拜寒冈事。宋公曰。 显宗癸卯。先祖自灵山季氏任所。归路入是院。盖为拜寒冈也。故其时门人赵根随行。书以展拜寒冈郑先生云。而此非先祖语也。
廿四日瞻庙。见神道碑亦在院侧。盖引玉山例也。发向红流洞。望见南下群山星罗棋置。而伽倻之山。挺特巀𡾦。俨然中处。如大丈夫之卓荦杰魁。独立万物之表者也。遍山松柏。柏子垂垂。邃林巨樾。绕蔓轇轕。时有虚籁自动。翠烟如浮。亦一胜观。抵笼山亭。一洞之峭壁铲崖。石之盘夷。流之奔崩。亦足擅胜。而瀑动雷轰。山谷响应。咫尺相间。不分人语。坐久忘言。嗒然会心而已。满石题名。皆行旅游子道人达官竞相题刻。刻上添刻。更无一字画插劖处。虽各欲其名不泐。亦何心哉。解驴背酒沃喉。使店人炊饭来亭上。同筐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6H 页
 异器。临席排分。䓀莄菜瓦沙钵。正好吃嚼。宋公笑曰。吾辈荀蔬之肠。在在饱得如是。蔡西山绝顶啖荠。尤觉其真趣也。余曰。崔文昌率妻子入此山。其事亦奇。若神仙之称。恐涉不经。至或谓孤云至今不死。有谁见之者。但其烟霞古洞。题品犹存。此其名不死耳。宋公曰。吾辈今日。亦去神仙不远。仍与诸生次孤云诗。日晚。海印寺僧以肩舆来待。暮抵寺。寺新罗哀庄王三年所创建。殿阁甚宏杰。
异器。临席排分。䓀莄菜瓦沙钵。正好吃嚼。宋公笑曰。吾辈荀蔬之肠。在在饱得如是。蔡西山绝顶啖荠。尤觉其真趣也。余曰。崔文昌率妻子入此山。其事亦奇。若神仙之称。恐涉不经。至或谓孤云至今不死。有谁见之者。但其烟霞古洞。题品犹存。此其名不死耳。宋公曰。吾辈今日。亦去神仙不远。仍与诸生次孤云诗。日晚。海印寺僧以肩舆来待。暮抵寺。寺新罗哀庄王三年所创建。殿阁甚宏杰。廿五日。往观藏经阁。阁为四十五间。高丽文宗。为刊八万大藏经于巨济岛。藏板于此云。宋公以有 宣教。未可淹迟。将速治发。遂拜辞。独东驰六十里。至延凤仲姊氏家留宿。
廿六日还家。
戊午十二月九日。以达城君橹南先祖墓坛碑记请文事。作蓝浦行。
十三日。至深川店宿。是日始得闻守宗斋宋公以是月一日丧逝。斯文益孤。惊悼不可言。
十五日。至石南。哭宋公几筵。与宋参判丈近洙。镇川郑雅海弼相晤。及晚发行。至儒城宿。
十八日。乘昏抵三溪。入谒肃斋赵公。欣倒叙晤。情爱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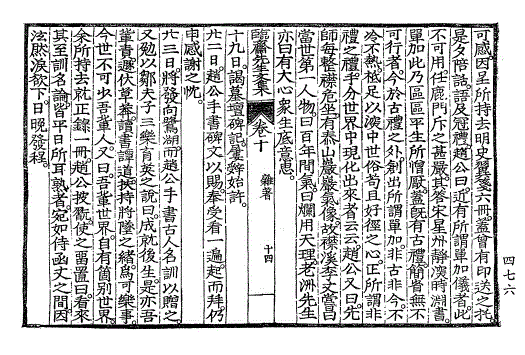 可感。因呈所持去明史翼笺六册。盖曾有印送之托。是夕陪话。语及冠礼。赵公曰。近有所谓单加仪者。此不可用。任鹿门斥之甚严。其答宋星州静深时渊书。单加此乃区区平生所憎厌。盖既有古礼。简省无不可行者。今于古礼之外。创出所谓单加。非古非今。不冷不热。祗足以深中世俗苟且好径之心。正所谓非礼之礼。手分世界中现化出来者云云。赵公又曰。先师每整襟危坐。有泰山岩岩气像。故襟溪李丈尝曰当世第一人物。曰百年间气。曰烂用天理。老洲先生亦曰有大心众生底意思。
可感。因呈所持去明史翼笺六册。盖曾有印送之托。是夕陪话。语及冠礼。赵公曰。近有所谓单加仪者。此不可用。任鹿门斥之甚严。其答宋星州静深时渊书。单加此乃区区平生所憎厌。盖既有古礼。简省无不可行者。今于古礼之外。创出所谓单加。非古非今。不冷不热。祗足以深中世俗苟且好径之心。正所谓非礼之礼。手分世界中现化出来者云云。赵公又曰。先师每整襟危坐。有泰山岩岩气像。故襟溪李丈尝曰当世第一人物。曰百年间气。曰烂用天理。老洲先生亦曰有大心众生底意思。十九日。谒墓坛碑记。屡辞始许。
廿二日。赵公手书碑文以赐。奉受看一遍。起而拜。乃申感谢之忱。
廿三日。将发向鹭湖。而赵公手书古人名训以赠之。又勉以邹夫子三乐育英之说曰。成就后生。是亦吾辈责。遁伏草莽。读书谭道。扶持将坠之绪。为可乐事。今世不可少吾辈人。又曰。吾辈世界。自有个别世界。余所持去就正录一册。赵公披玩。使之留置曰。看来其至训名论。皆平日所耳熟者。宛如侍函丈之间。因泫然泪欲下。日晚发程。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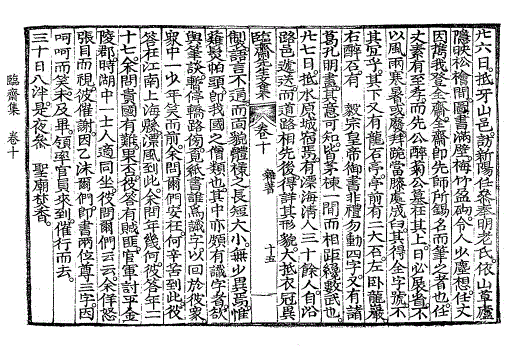 廿六日。抵牙山邑。访新阳任参奉明老氏。依山草庐隐映松桧间。图书满壁。梅竹盈砌。令人少尘想。任丈因携我登全斋。全斋即先师所锡名而笔之者也。任丈素有至孝。而先公醉菊公墓在其上。日必展省。不以风雨寒暑或废。拜跪当膝处成臼。其得全字号。不其宜乎。其下又有龙石亭。亭前有二大石。左卧龙岩。右醉石。有 毅宗皇帝御书非礼勿动四字。又有诸葛孔明画。其意可知。皆茅栋一间而相距才数武也。
廿六日。抵牙山邑。访新阳任参奉明老氏。依山草庐隐映松桧间。图书满壁。梅竹盈砌。令人少尘想。任丈因携我登全斋。全斋即先师所锡名而笔之者也。任丈素有至孝。而先公醉菊公墓在其上。日必展省。不以风雨寒暑或废。拜跪当膝处成臼。其得全字号。不其宜乎。其下又有龙石亭。亭前有二大石。左卧龙岩。右醉石。有 毅宗皇帝御书非礼勿动四字。又有诸葛孔明画。其意可知。皆茅栋一间而相距才数武也。廿七日。抵水原城宿焉。有漂海清人三十馀人。自沿路邑递送。而道路相先后。得详其形貌。大抵衣冠异制。语言不通。而面貌体样之长短大小。无少异焉。惟薙发帕头。即我国之僧类也。其中亦颇有识字者。欲与笔谈。暂停轿路傍。觅纸书谁为识字。以回于彼众。众中一少年笑而前。余问尔们安在。何辛苦到此。彼答在江南上海县。漂风到此。余问年几何。彼答年二十七。余问贵国有难。果否。彼答有贼匪。官军讨平金陵郡。时湖中一士人适同坐。彼问尔们云云。余佯怒张目而视。彼催谢。因乙沫尔们。即书两位尊三字。因呵呵而笑。未及毕。领率官员来到。催行而去。
三十日入泮。是夜参 圣庙焚香。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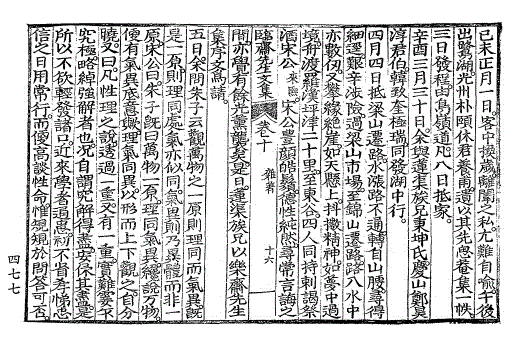 己未正月一日。客中换岁。离闱之私。尤难自喻。午后出鹭湖。光州朴颐休君养甫。遗以其先思庵集一帙。
己未正月一日。客中换岁。离闱之私。尤难自喻。午后出鹭湖。光州朴颐休君养甫。遗以其先思庵集一帙。三日发程。由鸟岭道。凡八日抵家。
辛酉三月三十日。余与莲渠族兄秉坤氏。庆山郑昊淳君伯。韩致奎极瑞。同发湖中行。
四月四日抵梁山迁路。水涨路不通。转自山腰。寻得细径。艰辛涉险。过梁山市场。至锦山迁路。路入水中亦数仞。又攀缘绝崖。如天悬上。抖擞精神。如梦中过境。舟渡罗汉坪津二十里。至东谷。四人同持刺谒祭酒宋公(来熙)。宋公礼颜皓须。德性纯然。寻常言诲之间。亦觉有馀光薰袭矣。是日。莲渠族兄以乐斋先生集序文为请。
五日。余问朱子云观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既是一原。则理同处气亦似同。气异则乃异体而非一原。宋公曰。朱子既曰万物一原。理同气异。才说万物。便有气异底意欤。理气同异。以形而上下观之。自分晓。又曰。凡性理之说。透过一重。又有一重。实难霎乍究极。略绰强解者也。况自谓究解得尽。安保其尽。是所以不欲轻发诸口。近来学者通患。初不省孝悌忠信之日用常行。而便高谈性命。惟规规于问答可否。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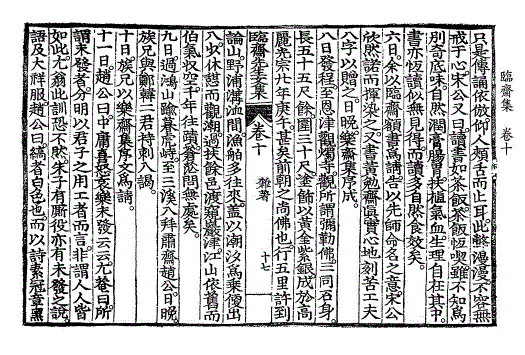 只是传诵依仿。仰人颊舌而止耳。此弊漫漫。不容无戒于心。宋公又曰。读书如茶饭。茶饭恒吃。虽不知为别奇底味。自然润膏肠胃。扶植气血。生理自在其中。书亦恒读似无见得。而读多自然食效矣。
只是传诵依仿。仰人颊舌而止耳。此弊漫漫。不容无戒于心。宋公又曰。读书如茶饭。茶饭恒吃。虽不知为别奇底味。自然润膏肠胃。扶植气血。生理自在其中。书亦恒读似无见得。而读多自然食效矣。六日。余以临斋额书为请。告以先师命名之意。宋公欣然诺而挥染之。又书黄勉斋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八字以赠之。日晚。乐斋集序成。
八日发程。至恩津观烛寺。观所谓弥勒佛。三同石身。长五十五尺馀。围三十尺。涂饰以黄金紫银。成于高丽光宗廿年庚午。甚矣前朝之尚佛也。行五里许到论山。野浦沟洫间。渔舶多往来。盖以潮汐为乘便出入。少休憩而观潮。过扶馀邑渡窥岩津。江山依旧而伯气收空。千年往迹。苍茫问无处矣。
九日。过鸿山踰暮虎峙。至三溪入拜肃斋赵公。日晚。族兄与郑韩二君持刺入谒。
十日。族兄以乐斋集序文为请。
十一日。赵公曰。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云云。尤庵曰。所谓未发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工者而言。非谓人人皆如此。尤翁此训恐不然。朱子有厮役亦有未发之说。语及大祥服。赵公曰。缟者白色也。而以诗素冠章黑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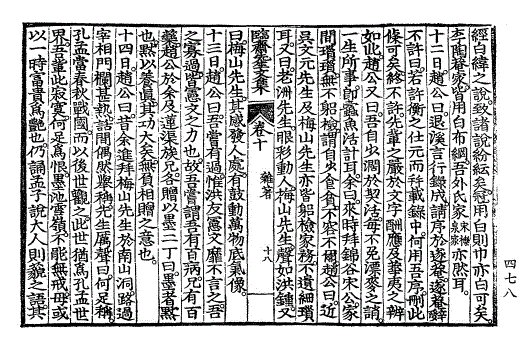 经白纬之说。致诸说纷纭矣。冠用白则巾亦白可矣。李陶庵家。皆用白布网。吾外氏家(宋栎泉家)亦然耳。
经白纬之说。致诸说纷纭矣。冠用白则巾亦白可矣。李陶庵家。皆用白布网。吾外氏家(宋栎泉家)亦然耳。十二日。赵公曰。退溪言行录成。请序于遂庵。遂庵辞不许曰。若许衡之仕元而并载录中。何用吾序。删此条可矣。终不许。先辈之严于文字酬应及华夷之辨如此。赵公又曰。吾自少阔于契活。每不免漂麦之诮。一生所事。即蠹鱼活计耳。余曰。来时拜锦谷宋公。家间琐琐。无不躬检。谓自少食贫。不容不尔。赵公曰。近吴文元先生及梅山先生亦皆躬检家务。不遗细琐耳。又曰。老洲先生。眼彩动人。梅山先生。声如洪钟。又曰。梅山先生。其感发人处。有鼓动万物底气像。
十三日。赵公曰。吾尝有过。惟洪友宪文靡不言之。吾之寡过。皆宪文之力也。故吾尝谓吾有百病。兄有百药。赵公于余及莲渠族兄。各赠以墨二丁曰。墨者默也。默以养真。其功大矣。无负相赠之意也。
十四日。赵公曰。昔余进拜梅山先生于南山洞。路过宰相门栏甚热。话间偶然举称。先生厉声曰。何足称。孔孟当春秋战国。而以后世观之。此世犹为孔孟世界。吾辈此寂寞。何足为恨。墨池雪岭。不能无戒。毋或以一时富贵为艳也。仍诵孟子说大人则藐之语。其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9H 页
 时惭愧之心。尚今不能忘。赵公又曰。老洲常言期会之间。大隐(李公凤秀)则赍若干馔。仅备一日之饥。仆从亦各赍囊资。规模凿凿。而梅山则优备橐糇。分吃之馀。波及诸仆与他人。两公气像。此可想得云。又曰。梅山先生。于并世诸贤。多有相见。老洲先生。独罕与游从。先生尝曰。若有儒贤出则一世奔竞。有眩鬻之嫌。故吾平生不见一贤。晚来有悔。先生又尝曰。古人云看好山。识好人。读好书。书者。是吾盖棺前可读。山水。虽筋力不给。犹可肩舆而往。在于好人。不与相待时不可失。先生此言甚好。
时惭愧之心。尚今不能忘。赵公又曰。老洲常言期会之间。大隐(李公凤秀)则赍若干馔。仅备一日之饥。仆从亦各赍囊资。规模凿凿。而梅山则优备橐糇。分吃之馀。波及诸仆与他人。两公气像。此可想得云。又曰。梅山先生。于并世诸贤。多有相见。老洲先生。独罕与游从。先生尝曰。若有儒贤出则一世奔竞。有眩鬻之嫌。故吾平生不见一贤。晚来有悔。先生又尝曰。古人云看好山。识好人。读好书。书者。是吾盖棺前可读。山水。虽筋力不给。犹可肩舆而往。在于好人。不与相待时不可失。先生此言甚好。十六日。余自鲁城入鸡岳。投宿于一旅店。是日观龙湫及我 太祖定基始役处。有大石廿个。中石六十馀个。皆有磨琢痕。
十七日。自东门峙历镇岑邑。至石南访宋雅秉琦昆弟。同出苏堤。观尤翁旧宅。又得假罗伊菜蓐食。
二十日还家。
排忧说(庚戌五月望)
乌有客。方夜读史倦。凭梧假寐。有一老叟颀硕癯矍。华发星星。岸巾杖藜。就与之揖曰。观子之容。轩轩其气也。施施其神也。近缘甚么关心。忳忳焉颎颎焉。如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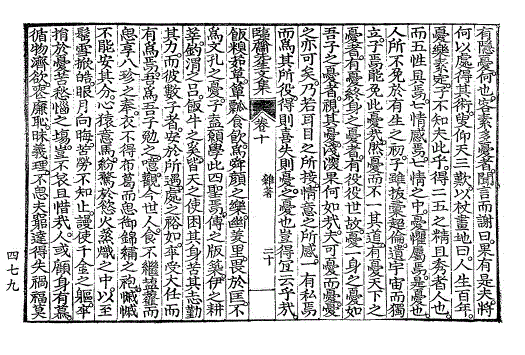 有隐忧。何也。客素多忧者。闻言而谢曰。果有是夫。将何以处得其术。叟仰天三叹。以杖画地曰。人生百年。忧乐素定。子不知夫此乎。得二五之精且秀者人也。而五性具焉。七情感焉。七情之中。忧惧属焉。是忧也。人所不免于有生之初。子虽拔汇超伦。遗宇宙而独立。子焉能免此忧哉。然忧而不一其道。有忧天下之忧者。有忧终身之忧者。有役役世故。忧一身之忧如吾子之忧者。视其忧。浅深果何如哉。夫可忧而忧。忧之亦可矣。乃若耳目之所接。情意之所感。一有私焉而为其所役。得则喜失则忧。之忧也岂得宜云乎哉。饭糗茹草。箪瓢食饮。为舜颜之乐。幽羑里。畏于匡。不为文孔之忧。子盍愿学此四圣焉。傅之版筑。伊之耕莘。钓渭之吕。饭牛之奚。皆天之使困其身苦其志勤其力。而彼数子者。安于所遇。处之裕如。卒受大任而有为焉。吾为吾子勉之。噫。观今世人。食不继盐齑而思享八珍之奉。衣不得布葛而思御锦绣之袍。戚戚不能安其分。心猿意马。纷骛于欲火蒸炽之中。以至鬓雪掀皓。眼月向晦。苦劳不知止。谩使千金之躯。卒捐于忧苦愁恼之场。岂不哀且惜哉。人或顾身有慕。循物济欲。丧廉耻。昧义理。不思夫穷达得失祸福莫
有隐忧。何也。客素多忧者。闻言而谢曰。果有是夫。将何以处得其术。叟仰天三叹。以杖画地曰。人生百年。忧乐素定。子不知夫此乎。得二五之精且秀者人也。而五性具焉。七情感焉。七情之中。忧惧属焉。是忧也。人所不免于有生之初。子虽拔汇超伦。遗宇宙而独立。子焉能免此忧哉。然忧而不一其道。有忧天下之忧者。有忧终身之忧者。有役役世故。忧一身之忧如吾子之忧者。视其忧。浅深果何如哉。夫可忧而忧。忧之亦可矣。乃若耳目之所接。情意之所感。一有私焉而为其所役。得则喜失则忧。之忧也岂得宜云乎哉。饭糗茹草。箪瓢食饮。为舜颜之乐。幽羑里。畏于匡。不为文孔之忧。子盍愿学此四圣焉。傅之版筑。伊之耕莘。钓渭之吕。饭牛之奚。皆天之使困其身苦其志勤其力。而彼数子者。安于所遇。处之裕如。卒受大任而有为焉。吾为吾子勉之。噫。观今世人。食不继盐齑而思享八珍之奉。衣不得布葛而思御锦绣之袍。戚戚不能安其分。心猿意马。纷骛于欲火蒸炽之中。以至鬓雪掀皓。眼月向晦。苦劳不知止。谩使千金之躯。卒捐于忧苦愁恼之场。岂不哀且惜哉。人或顾身有慕。循物济欲。丧廉耻。昧义理。不思夫穷达得失祸福莫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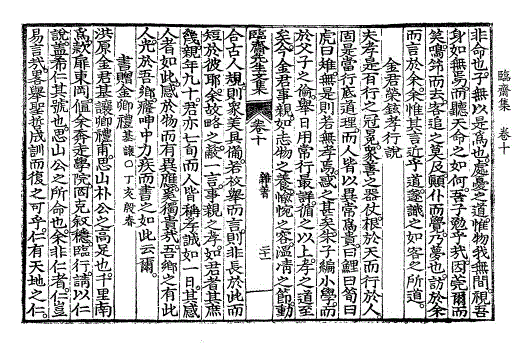 非命也。子无以是为也。处忧之道。惟物我无间。视吾身如无焉。而听天命之如何。吾子勉乎哉。因莞尔而笑。鸣筇而去。客追之莫及。颠仆而觉。乃梦也。访于余而言于余。余惟其言近乎道。遂识之如客之所道。
非命也。子无以是为也。处忧之道。惟物我无间。视吾身如无焉。而听天命之如何。吾子勉乎哉。因莞尔而笑。鸣筇而去。客追之莫及。颠仆而觉。乃梦也。访于余而言于余。余惟其言近乎道。遂识之如客之所道。金君荣铉孝行说
夫孝是百行之冠冕。众善之器仗。根于天而行于人。固是当行底道理。而人皆以异常为贵。曰鲤曰笋曰虎曰雉。无是则若无孝焉。惑之甚矣。朱子编小学。而于父子之伦。举日用常行最详。循之以上。孝之道至矣。今金君事亲。如志物之养。愉惋之容。温凊之节。动合古人规。则众美具备。若枚举而言。则非长于此而短于彼耶。余故略之。蔽一言。事亲之孝。如君者其庶几。亲年九十。君亦七旬而人皆称孝诚如一日。其感人者如此。感于物而有异应。奚独贵哉。吾乡之有此人。光于吾乡。癃呻中力疾而书之如此云尔。
书赠金卿礼(基让○丁亥殷春)
洪原金君基让卿礼甫。思山朴公之高足也。千里南为。款扉东冈。值余奔走学院。罔克叙稳。临行。请以仁说。盖希仁其号也。思山公之所命也。余非仁者。仁岂易言哉。略举圣哲成训而复之可乎。仁有天地之仁。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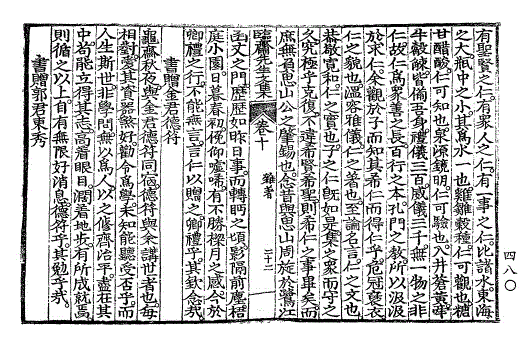 有圣贤之仁。有众人之仁。有一事之仁。比诸水。东海之大。瓶中之小。其为水一也。鸡雏谷种。仁可观也。糖甘醋酸。仁可知也。泉源镜明。仁可验也。入井苍黄。牵牛觳觫。皆备吾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之非仁。故仁为众善之长。百行之本。孔门之教。所以汲汲于求仁。余观于子而知其希仁而得仁乎。危冠袖衣。仁之貌也。温容雅仪。仁之著也。至论名言。仁之文也。恭敬宽和。仁之实也。子之仁既如是。集之众而守之久。究极乎克复。不违希贤希圣。则希仁之事毕矣。而庶无负思山公之肇锡也。念昔与思山周旋于鹭江函丈之门。历历如昨日事。而转眄之顷。影隔前尘。梧庭小园。日暮春初。俛仰嘘唏。有不胜梁月之感。今于卿礼之行。不能无言。言仁以赠之。卿礼乎。其钦念哉。
有圣贤之仁。有众人之仁。有一事之仁。比诸水。东海之大。瓶中之小。其为水一也。鸡雏谷种。仁可观也。糖甘醋酸。仁可知也。泉源镜明。仁可验也。入井苍黄。牵牛觳觫。皆备吾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之非仁。故仁为众善之长。百行之本。孔门之教。所以汲汲于求仁。余观于子而知其希仁而得仁乎。危冠袖衣。仁之貌也。温容雅仪。仁之著也。至论名言。仁之文也。恭敬宽和。仁之实也。子之仁既如是。集之众而守之久。究极乎克复。不违希贤希圣。则希仁之事毕矣。而庶无负思山公之肇锡也。念昔与思山周旋于鹭江函丈之门。历历如昨日事。而转眄之顷。影隔前尘。梧庭小园。日暮春初。俛仰嘘唏。有不胜梁月之感。今于卿礼之行。不能无言。言仁以赠之。卿礼乎。其钦念哉。书赠金君德符
龟斋秋夜。与金君德符同宿。德符与余讲世者也。每相对。爱其资器煞好。劝令为学。未知能听受否乎。而人生斯世。非学问。无以为人。以之修齐治平。尽在其中。苟能立得其志。高着眼目。阔着地步。有所成就焉。则循之以上。自有无限好消息。德符乎。其勉乎哉。
书赠郭君东秀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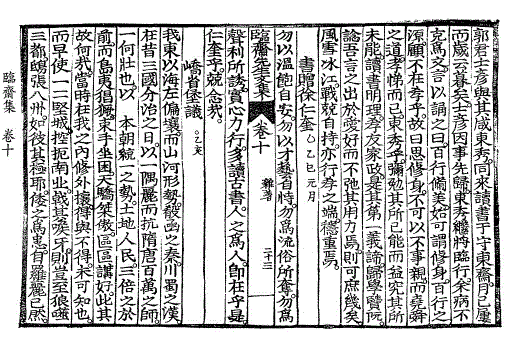 郭君士彦与其咸东秀。同来读书于守东斋。月已屡而岁云暮矣。士彦因事先归。东秀继将临行。余病不克为文。言以诵之曰。百行备美。始可谓修身。百行之源。顾不在孝乎。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东秀乎。弥勉其所已能而益究其所未能。读书明理。孝友家政。是其第一义谛。归学贤阮。谂吾言之出于爱好而不弛其用力焉。则可庶几矣。风雪冰江。战兢自持。亦行孝之端。稳重焉。
郭君士彦与其咸东秀。同来读书于守东斋。月已屡而岁云暮矣。士彦因事先归。东秀继将临行。余病不克为文。言以诵之曰。百行备美。始可谓修身。百行之源。顾不在孝乎。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东秀乎。弥勉其所已能而益究其所未能。读书明理。孝友家政。是其第一义谛。归学贤阮。谂吾言之出于爱好而不弛其用力焉。则可庶几矣。风雪冰江。战兢自持。亦行孝之端。稳重焉。书赠徐仁奎(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圭'로 되어 있다.乙巳元月)
勿以温饱自安。勿以才艺自恃。勿为流俗所夺。勿为声利所诱。实心力行。多读古书。人之为人。即在乎是。仁奎乎。兢念哉。
峤省堡议(乙亥)
我东以海左偏壤。而山河形势。殽函之秦。川蜀之汉。在昔三国分治之日。以一隅丽而抗隋唐百万之师。一何壮也。以 本朝统一之势。土地人民。三倍之于前。而岛夷猖獗。束手坐困。天骄桀傲。区区讲好。此其故何哉。当时在我之内修外攘。得与不得。未可知也。而早使一二坚城。控扼南北。戟其喉牙。则岂至狼噬三都。鸱张八州。如彼其极耶。倭之为患。自罗丽已然。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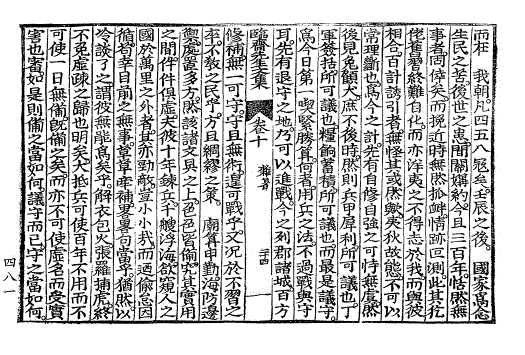 而在 我朝。凡四五入寇矣。壬辰之后。 国家为念生民之苦。后世之患。间关媾约。今且三百年。恬然无事者。固倖矣。而挽近时无然㧓(一作抓)衅。情迹叵测。此其犵佬旧习终难自化。而亦洋夷之不得志于我。而与彼相合。百计诱引者。无怪其或然欤。夷狄故态。不可以常理断也。为今之计。先有自修自强之可恃无虞。然后见兔顾犬。庶不后时。然则兵甲犀利。所可议也。丁军签括。所可议也。粮饷蓄积。所可议也。而最是议守。为今日第一吃紧胜算。何者。用兵之法。不过战与守耳。先有退守之地。乃可以进战。今之列郡诸城。百方修补。无一可守。守且无术。遑可战乎。又况于不习之卒。不教之民乎。方且绸缪之策。 庙算申勤。海防边御。处置多方。然该诸文具之上。色色皆备。究其实用之间。件件俱虚。夫彼十年鍊兵。千艘浮海。欲窥人之国于万里之外者。其亦劲敌。岂小小哉。而乃偷怠因循。苟幸目前之无事。草草牵补。略略句当乎。犹然。以冷谈了之。谓彼无能为矣乎。解衣包火。张罗捕虎。终不免虚疏之归也明矣。大抵兵可使百年不用而不可使一日无备。既备之矣。而亦不可使虚名而受实害也审。如是则备之当如何。议守而已。守之当如何。
而在 我朝。凡四五入寇矣。壬辰之后。 国家为念生民之苦。后世之患。间关媾约。今且三百年。恬然无事者。固倖矣。而挽近时无然㧓(一作抓)衅。情迹叵测。此其犵佬旧习终难自化。而亦洋夷之不得志于我。而与彼相合。百计诱引者。无怪其或然欤。夷狄故态。不可以常理断也。为今之计。先有自修自强之可恃无虞。然后见兔顾犬。庶不后时。然则兵甲犀利。所可议也。丁军签括。所可议也。粮饷蓄积。所可议也。而最是议守。为今日第一吃紧胜算。何者。用兵之法。不过战与守耳。先有退守之地。乃可以进战。今之列郡诸城。百方修补。无一可守。守且无术。遑可战乎。又况于不习之卒。不教之民乎。方且绸缪之策。 庙算申勤。海防边御。处置多方。然该诸文具之上。色色皆备。究其实用之间。件件俱虚。夫彼十年鍊兵。千艘浮海。欲窥人之国于万里之外者。其亦劲敌。岂小小哉。而乃偷怠因循。苟幸目前之无事。草草牵补。略略句当乎。犹然。以冷谈了之。谓彼无能为矣乎。解衣包火。张罗捕虎。终不免虚疏之归也明矣。大抵兵可使百年不用而不可使一日无备。既备之矣。而亦不可使虚名而受实害也审。如是则备之当如何。议守而已。守之当如何。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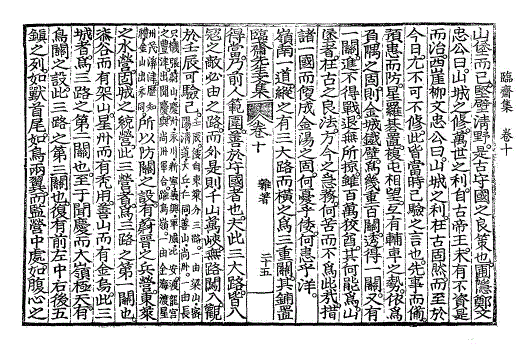 山堡而已。坚壁清野。是古守国之良策也。圃隐郑文忠公曰。山城之修。万世之利。自古帝王。未有不资是而治。西崖柳文忠公曰。山城之利。在古固然。而至于今日。尤不可不修。此皆当时已验之言也。先事而备。预患而防。星罗棋置。复屯相望。互有辅车之势。依为负隅之固。则金城铁壁。为几重百关。透得一关。又有一关。进不得战。退无所掠。虽百万狡酋。其何能为。山堡者。在古之良法。方今之急务。何苦而不为此哉。措诸一国而便成金汤之固。何忧乎倭。何患乎洋。
山堡而已。坚壁清野。是古守国之良策也。圃隐郑文忠公曰。山城之修。万世之利。自古帝王。未有不资是而治。西崖柳文忠公曰。山城之利。在古固然。而至于今日。尤不可不修。此皆当时已验之言也。先事而备。预患而防。星罗棋置。复屯相望。互有辅车之势。依为负隅之固。则金城铁壁。为几重百关。透得一关。又有一关。进不得战。退无所掠。虽百万狡酋。其何能为。山堡者。在古之良法。方今之急务。何苦而不为此哉。措诸一国而便成金汤之固。何忧乎倭。何患乎洋。岭南一道。纵之有三大路而横之为三重关。其铺置得当。乃前人范围。善于守国者也。夫此三大路。皆入寇之敌必由之路。而外是则千山万峡。无路闯入。观于壬辰可验已。(壬辰。倭自东莱分三路。一由梁山,密阳,清道,大丘,仁同,善山,尚州。一由长只,机张,蔚山,庆州,永川,新宁,义兴,军威,比安。渡龙宫之礼津。出闻庆。与尚州军合。踰鸟岭。一由金海渡星州茂溪津。历知礼,金山出永同。)所以防关之设。有蔚晋之兵营。东莱之水营。固城之统营。此三营者。为三路之第一关也。㓒谷而有架山。星州而有秃用。善山而有金乌。此三城者。为三路之第二关也。至于闻庆而大岭极天。有鸟关之设。此三路之第三关也。复有前左中右后五镇之列。如兽首尾。如鸟两翼。而监营中处。如腹心之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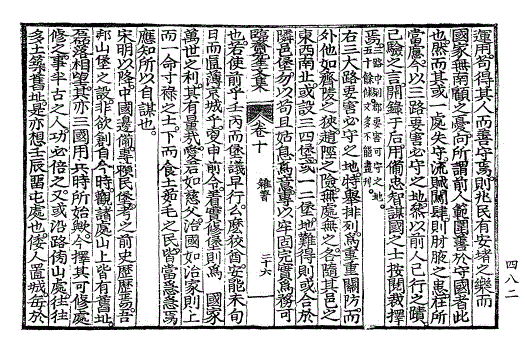 运用。苟得其人而善守焉。则兆民有安堵之乐而 国家无南顾之忧。向所谓前人范围善于守国者此也。然而其或一处失守。流贼闯肆。则肘腋之患。在所当虑。今以三路要害必守之地。参以前人已行之迹。已验之言。开录于后。用备忠智谋国之士按阅裁择焉。(三路中列郡要害可守之地。五十馀条。文多不能尽刊。)
运用。苟得其人而善守焉。则兆民有安堵之乐而 国家无南顾之忧。向所谓前人范围善于守国者此也。然而其或一处失守。流贼闯肆。则肘腋之患。在所当虑。今以三路要害必守之地。参以前人已行之迹。已验之言。开录于后。用备忠智谋国之士按阅裁择焉。(三路中列郡要害可守之地。五十馀条。文多不能尽刊。)右三大路要害必守之地。特举排列。为重重关防。而外他如齐陵之狭。赵陉之险。无处无之。各随其邑之东西南北。或设三四堡。或一二堡。地难得则或合于邻邑堡。勿以苟且姑息为意。专以牢固完实为务可也。若使前乎壬丙而堡议早行。幺么狡酋。安能未旬日而直薄京城乎。更申前令。着实修堡则为 国家万世之利。其有量哉。爱君如慈父。治国如治家则上而一命寸禄之士。下而食土茹毛之民。皆当急急焉应知所以自谋也。
宋明以降。中国边备。专赖民堡。考之前史历历焉。吾邦山堡之设。非欲创自今时。观诸处山上皆有旧址。磊落相望。其亦三国用兵时所始欤。今择其可修处修之。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或沿路傍山处。往往多土筑旧址。是亦想壬辰留屯处也。倭人置城。每于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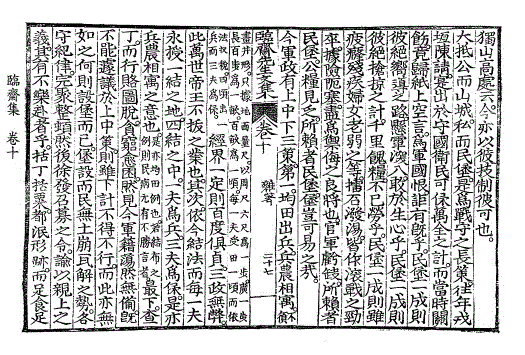 独山高处云。今亦以彼技制彼可也。
独山高处云。今亦以彼技制彼可也。大抵公而山城。私而民堡。是为战守之长策。往年戎垣陈请。寔出于守国卫民可保万全之计。而当时关饬。竟归纸上空言。为军国恨。讵有既乎。民堡一成则彼绝向导之路。悬军深入。敢于生心乎。民堡一成则彼绝抢掠之计。千里馈粮。不已劳乎。民堡一成则虽疲癃残疾妇女老弱之等。擂石泼汤。皆作滚战之劲卒。据险阨塞。尽为御侮之良将也。官军亏缺。所赖者民堡。公粮见乏。所赖者民堡。堡岂可易之哉。
今军政有上中下三策。第一。均田出兵。兵农相寓。(不须画井形。只据地面量尺。以周尺六尺为一步。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每一夫受田一顷而依法收税。四顷出一兵而三夫为保。)经界一定则百度俱贞。三政无弊。此万世帝王不拔之业也。其次。依今结法而每一夫永授一结之地。四结之中。一夫为兵。三夫为保。是亦兵农相寓之意也。(是亦均田例也。若结布之例则民病尤有不胜言者。)最下。查丁。而行赂图脱。贫穷愈困。然见今军籍荡然无备。既不能遽议于上中策。则虽下计不得不行。而此亦无如之何则设堡而已。堡设而民无土崩瓦解之势。各守纪律。完聚整顿然后徐发召募之令。谕以亲上之义。其有不乐赴者乎。括丁括粟。都泯形迹。而足食足
临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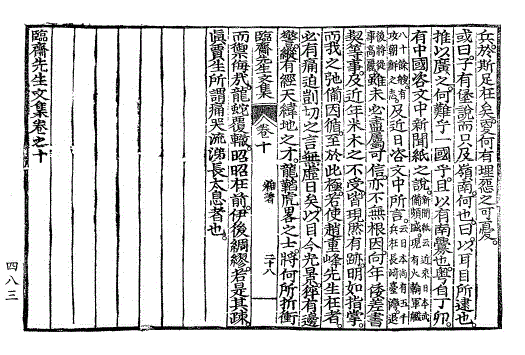 兵。于斯足在矣。更何有埋怨之可忧。
兵。于斯足在矣。更何有埋怨之可忧。或曰。子有堡说而只及岭南。何也。曰。以耳目所逮也。推以广之。何难乎一国乎。且以有南衅也。粤自丁卯。有中国咨文中新闻纸之说。(新闻纸云近来日本武备颇盛。现有火轮军舰八十馀艘。有攻朝鲜之志。)及近日咨文中所言。(云日本尚有五千兵在长崎台湾。退后将从事高丽。)虽未必尽属可信。亦不无根因。向年倭差书契等事。及近年米木之不受。皆现然有迹。明如指掌。而我之弛备因循。至于此极。若使赵重峰先生在者。必有痛迫剀切之言无虚日矣。以目今光景。猝有边警。纵有经天纬地之才。龙韬虎略之士。将何所折冲而御侮哉。龙蛇覆辙。昭昭在前。伊后绸缪。若是其疏。真贾生所谓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