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x 页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记
记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4H 页
 吾山堂重建记
吾山堂重建记武夷之六六洞天。名于天下。而晦庵夫子精舍之咏曰居然我泉石。清凉之十二峰峦。名于海东。而退陶先生游山之录曰实为吾家山。噫之山也。天作地设。元气扶舆。以待夫千百岁之后者。其意岂偶然哉。于是而我两夫子出。尝于游赏之暇。占取境界。以寓其仁智无穷之乐。则彼玉立于烟霞之外。矗矗而尖尖者。皆吾几案之物耳。万世吾道之托。不于玆山而更于何处也。惟是武夷之屋。成于当日。清凉之堂。起于后贤。盖所谓诗成而屋未者也。至健陵壬辰。一方衿绅。询谋远迩。始建三架之堂于紫霄峰下。追成先生之遗志。俯循多士之舆情。因以为讲道兴学之所。而扁之曰吾山堂。盖取游录吾家山之语也。自是濂亭之风月无边。鹿洞之弦诵相闻。半亩宫墙。俨然为海东之武夷。则吾党小子景行之忱。得有所向。而不迷于吾家之路矣。不幸柔兆之变。便同龙汉之劫。玉石俱烬。堂室荡然。将使荆棘蓬蒿。浸及于昌平之闾。则天岂欲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4L 页
 斯文之尽丧耶。抑亦气数之适然也。呜呼。程伯子颜乐亭之铭曰井不忍废。地不忍荒。呜呼正学。其何可忘。噫今日章甫。皆先生之遗徒也。忍以气数之适然。而一日忘图复之志乎。乃者本孙某某等。与乡道儒绅。衋然恸伤。发虑规画。扫一壑之烟煤。复旧日之规制。前后费日若干。小大经用亦若干。而轮奂告功。山川出色。岂或鬼神之阴来相之者欤。凡堂之制。皆袭乎陶山。而前退数楹。所以增其广也。新穿小塘。所以兼其美也。曰云栖曰止宿曰吾山。皆以旧号仍之。曰观善曰幽贞曰净友。皆以新扁揭之。盖秩秩尔井井尔。既而本孙晚舆君撰成吾山志一统。以备故事。因责道和以记其事。自顾晚生蔑识。虽数行记语何敢焉。旋又念道和之愚。夙慕先生之风。尝一登陶山。瞻肃于尚德之庙。俛仰于天渊之台。愿为浴沂之童子而不可得。则第有忾然之叹而已。今以区区姓名。猥托于夫子之堂。何如其荣幸也。玆敢不揆而拜受。因又复之曰。今玆之役。寔出于尊卫先生。而窃恐尊卫之道。不可曰尽于是也。幸使吾党君子。益读先生之书。益讲先生之学。摄齐升堂。宛承申夭之气象。周旋
斯文之尽丧耶。抑亦气数之适然也。呜呼。程伯子颜乐亭之铭曰井不忍废。地不忍荒。呜呼正学。其何可忘。噫今日章甫。皆先生之遗徒也。忍以气数之适然。而一日忘图复之志乎。乃者本孙某某等。与乡道儒绅。衋然恸伤。发虑规画。扫一壑之烟煤。复旧日之规制。前后费日若干。小大经用亦若干。而轮奂告功。山川出色。岂或鬼神之阴来相之者欤。凡堂之制。皆袭乎陶山。而前退数楹。所以增其广也。新穿小塘。所以兼其美也。曰云栖曰止宿曰吾山。皆以旧号仍之。曰观善曰幽贞曰净友。皆以新扁揭之。盖秩秩尔井井尔。既而本孙晚舆君撰成吾山志一统。以备故事。因责道和以记其事。自顾晚生蔑识。虽数行记语何敢焉。旋又念道和之愚。夙慕先生之风。尝一登陶山。瞻肃于尚德之庙。俛仰于天渊之台。愿为浴沂之童子而不可得。则第有忾然之叹而已。今以区区姓名。猥托于夫子之堂。何如其荣幸也。玆敢不揆而拜受。因又复之曰。今玆之役。寔出于尊卫先生。而窃恐尊卫之道。不可曰尽于是也。幸使吾党君子。益读先生之书。益讲先生之学。摄齐升堂。宛承申夭之气象。周旋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5H 页
 入户。如闻明诚之旨诀。使先生之道。不坠在人。而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则彼一时之狂氛虐焰。自当清廓于天日之下。而斯堂也亦将共天壤而无疆矣。荀卿子之言曰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窃为佥君子诵之。后学闻韶金道和谨记。
入户。如闻明诚之旨诀。使先生之道。不坠在人。而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则彼一时之狂氛虐焰。自当清廓于天日之下。而斯堂也亦将共天壤而无疆矣。荀卿子之言曰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窃为佥君子诵之。后学闻韶金道和谨记。西山书堂记
岭之南。有州曰咸安。咸之西。有山曰伯夷。此何以称焉。地之相距。万有馀里。世之相后千有馀岁。而之山也冒是号而不辞。岂其巍崒不拔之势。有似乎举世非之而独行不顾者欤。抑亦天作而地设。以待夫千百岁之其人也欤。呜呼异矣。国家 庄陵之际。渔溪先生赵公。出于咸州。而终老于玆山之下。迹其终始。盖所称伯夷之俦也。当乙亥禅受。天与人归。而有六臣者死而不悔。又有六臣者生而自靖。先生即其一也。先生之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故一揖庠宫。渔钓自托。则隐然有周粟不食之义也。九日登高。慷慨悲吟。则忾然有采薇作歌之怀。服上王三年而不顾人之是非。约规楼相会而誓一片之心期。则是又伯夷之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5L 页
 所未有也。幸而生于夫子之世。则安知不曰求仁而得仁乎。尝有题其墓者曰使西山二子。生于当日。必将开心曲仰天长吁。真可谓知公之心矣。噫玆山之名。得先生而不虚。先生之节。与是山而无穷。则造物所以施设于此。而预期于千百世之前者。其意岂偶然哉。后世之人。苟欲羹墙以寓其慕。尸祝以尊其道。则舍是山而更于何处也。 明陵癸未。一省闻风之徒。相率趍趍。直其地而建祠。并五先生而侑之。即所谓西山书院是也。山空月白。陟降之灵如在。水动花落。叹息之声如闻。将使天下之人。洒然一变。家清节而户卓行矣。运迫元二。毁籍延及。明宫斋室。蓁莽于芜没。斲桷仓楹。瓦砾于狼籍。呜呼。天理人情。有不当然者。今以朱夫子修复白鹿之遗意观之。则忍可以一日湮废乎。至 今上辛丑。公议奋发。乃即旧而新之。因院而堂之。上而不碍邦制。下而无废贤躅。东西为堂凡几十架。南北为室亦数十架。工殚力而增其饰。众趍事而乐其成。盖渠渠尔秩秩尔。粤瞻鹰岩。则四尺斧堂。宛在于寂历之中。顾瞻渔台。则一丝清风。飒然乎髣髴之际。先生烈烈之灵。于此于彼。而当日
所未有也。幸而生于夫子之世。则安知不曰求仁而得仁乎。尝有题其墓者曰使西山二子。生于当日。必将开心曲仰天长吁。真可谓知公之心矣。噫玆山之名。得先生而不虚。先生之节。与是山而无穷。则造物所以施设于此。而预期于千百世之前者。其意岂偶然哉。后世之人。苟欲羹墙以寓其慕。尸祝以尊其道。则舍是山而更于何处也。 明陵癸未。一省闻风之徒。相率趍趍。直其地而建祠。并五先生而侑之。即所谓西山书院是也。山空月白。陟降之灵如在。水动花落。叹息之声如闻。将使天下之人。洒然一变。家清节而户卓行矣。运迫元二。毁籍延及。明宫斋室。蓁莽于芜没。斲桷仓楹。瓦砾于狼籍。呜呼。天理人情。有不当然者。今以朱夫子修复白鹿之遗意观之。则忍可以一日湮废乎。至 今上辛丑。公议奋发。乃即旧而新之。因院而堂之。上而不碍邦制。下而无废贤躅。东西为堂凡几十架。南北为室亦数十架。工殚力而增其饰。众趍事而乐其成。盖渠渠尔秩秩尔。粤瞻鹰岩。则四尺斧堂。宛在于寂历之中。顾瞻渔台。则一丝清风。飒然乎髣髴之际。先生烈烈之灵。于此于彼。而当日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6H 页
 之苦心贞节。亦可以想见其万一矣。何必待太史氏蚕室之传而后。知伯夷之为伯夷也哉。嗟乎。道和亦兴起之徒也。尝有执鞭之愿。今于本孙诸君子之请。谨书其所感。作西山书堂记。
之苦心贞节。亦可以想见其万一矣。何必待太史氏蚕室之传而后。知伯夷之为伯夷也哉。嗟乎。道和亦兴起之徒也。尝有执鞭之愿。今于本孙诸君子之请。谨书其所感。作西山书堂记。忠庄公大田李先生墓所斋阁记
昔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而天下称之。万世传之。盖以天彝民衷之殄灭佗不得者然也。向使二子体魄之藏。兀然在首阳之上。则天下万世之所以感激爱慕而崇奉之者。又恶得以已哉。武王封比干之墓。夫子书延陵之碣。观于此而益知仁贤之墓。如是其重也。呜呼。忠庄公大田先生。即向所称二子之伦。而事之难处。抑有甚焉。当 景泰乙亥。天命人心。已有所归。而先生独以尽忠所事为义。始则慷慨许心于锦城大君珊瑚之赠。末乃从容赴蹈于成朴诸贤汤火之馀。但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则其身后之收骸与未。初非先生之所恤也。先生尝祭冶隐之墓曰。植纲常于既坠。励士风于靡然。安知非当日自道之辞乎。先生之弟副使公。尝冒万死收遗骼。反瘗于永阳先垄之傍。其坎负丑也。其地丹崖也。而鲁人之讳已久。寒山之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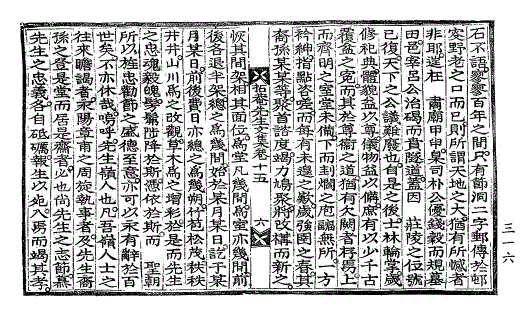 石不语。寥寥百年之间。只有节洞二字邮传于村叟野老之口而已。则所谓天地之大。犹有所憾者非耶。𨓏在 肃庙甲申。臬司朴公优钱谷而规墓田。邑宰吕公治碣而贲隧道。盖因 庄陵之位号已复。天下之公议难废也。自是之后。士林轮掌。岁修祀典。体貌益以尊。仪物益以备。庶有以少千古覆盆之冤。而其于尊卫之道。犹有欠阙者存焉。上而齐明之室堂未备。下而刲爓之庖副无所。一方衿绅。指点咨嗟。而每有未遑之叹。岁强圉之春。其裔孙某某等。聚首咨度。竭力鸠聚。将改构而新之。恢其间架。相其面位。为堂凡几间。为室亦几间。前后各退半架。总之为几间。始于某月某日。讫于某月某日。前后费日亦总之为几朔。竹苞松茂。秩秩井井。山川为之改观。草木为之增彩。于是而先生之忠魂毅魄。髣髴陟降于斯。凭依于斯。而 圣朝所以旌忠劝节之盛德至意。亦可以永有辞于百世矣。不亦休哉。呜呼。先生岭人也。凡吾岭人士之往来瞻谒者。永阳章甫之周旋执事者。及先生裔孙之登是堂而居是斋者。必也尚先生之志节。慕先生之忠义。各自砥砺。报生以死。入焉而竭其孝。
石不语。寥寥百年之间。只有节洞二字邮传于村叟野老之口而已。则所谓天地之大。犹有所憾者非耶。𨓏在 肃庙甲申。臬司朴公优钱谷而规墓田。邑宰吕公治碣而贲隧道。盖因 庄陵之位号已复。天下之公议难废也。自是之后。士林轮掌。岁修祀典。体貌益以尊。仪物益以备。庶有以少千古覆盆之冤。而其于尊卫之道。犹有欠阙者存焉。上而齐明之室堂未备。下而刲爓之庖副无所。一方衿绅。指点咨嗟。而每有未遑之叹。岁强圉之春。其裔孙某某等。聚首咨度。竭力鸠聚。将改构而新之。恢其间架。相其面位。为堂凡几间。为室亦几间。前后各退半架。总之为几间。始于某月某日。讫于某月某日。前后费日亦总之为几朔。竹苞松茂。秩秩井井。山川为之改观。草木为之增彩。于是而先生之忠魂毅魄。髣髴陟降于斯。凭依于斯。而 圣朝所以旌忠劝节之盛德至意。亦可以永有辞于百世矣。不亦休哉。呜呼。先生岭人也。凡吾岭人士之往来瞻谒者。永阳章甫之周旋执事者。及先生裔孙之登是堂而居是斋者。必也尚先生之志节。慕先生之忠义。各自砥砺。报生以死。入焉而竭其孝。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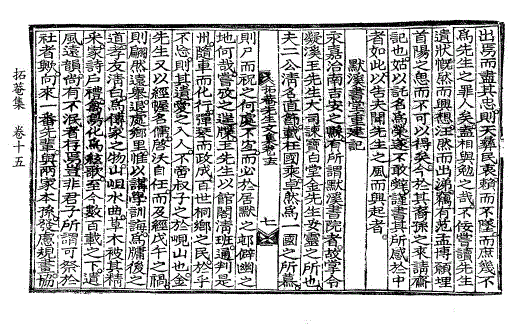 出焉而尽其忠。则天彝民衷。赖而不坠。而庶几不为先生之罪人矣。盍相与勉之哉。不佞尝读先生遗状。慨然而兴想。汪然而出涕。窃有范孟博愿埋首阳之思而不可以得矣。今于其裔孙之来请斋记也。姑以托名为荣。遂不敢辞。谨书其所感于中者如此。以告夫闻先生之风而兴起者。
出焉而尽其忠。则天彝民衷。赖而不坠。而庶几不为先生之罪人矣。盍相与勉之哉。不佞尝读先生遗状。慨然而兴想。汪然而出涕。窃有范孟博愿埋首阳之思而不可以得矣。今于其裔孙之来请斋记也。姑以托名为荣。遂不敢辞。谨书其所感于中者如此。以告夫闻先生之风而兴起者。默溪书堂重建记
永嘉治南吉安之县。有所谓默溪书院者。故掌令凝溪玉先生,大司谏宝白堂金先生妥灵之所也。夫二公清名直节。载在国乘。卓然为一国之所慕。则尸而祝之何处不宜。而必于居默之村僻幽之地何哉。尝考之𨓏牒。玉先生以馆阁清班。通判是州。随车而化行。弹琴而政成。百世桐乡之民。于乎不忘。则其遗爱之入人。不啻叔子之于岘山也。金先生又以经幄名儒。启沃自任。而及经戊午之祸。则翩然远举。退处乡里。惟以讲学训诲。为牖后之道。孝友清白。为传家之物。山岨水曲。草木被其精采。家诗户礼。禽鸟化为弦歌。至今数百载之下。遗风远韵。尚有不泯者存焉。岂非君子所谓可祭于社者欤。向来一番先辈。与两家本孙。发虑规画。协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7L 页
 力营设。图所以崇德尚贤。而永为后人之矜式。其刱建在 肃庙辛巳年间。而后贤继起。仪物渐增。仓楹斲桷之制。灿然而毕备。斋楼庖副之所。秩然而有序。笾豆牲醴于斯。揖让兴俯于斯。吾党之士庶几有所瞻依。而羹于食而墙于立矣。天道有显晦之几。王政有损益之宜。不幸庚午毁籍。遍及本院。神板既已荒原矣。栋宇亦已墟莽矣。但见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则远迩襟绅之行过洞门者。顾安得三遇如常。而不为之彷徨怵惕也哉。后二十馀年乙未。一方人士。因彝衷之所同。即其旧址而更谋数间屋子。上而不僭于邦制。下而少伸于舆情。始于六月某甲。讫于九月某甲。堂室凡若干楹。库厨凡若干架。得日凡四阅朔。盖士林与本孙之诚力。可谓两尽而无馀矣。虽然盖闻尊卫之道。不在于祠宇崇奉。而在乎读其书讲其道。今距二先生之世远矣。杞宋虽无徵。而 国朝清白吏之案。西厓先生永慕之编。班班可据。不可曰寂寥。则幸使诸君子之居于是邦者。因其所可据而想其所无徵。体先生之心法。尚先生之风节。清白以持其身。忠直以事其君。益自砥砺。如恐不及。则是乃所
力营设。图所以崇德尚贤。而永为后人之矜式。其刱建在 肃庙辛巳年间。而后贤继起。仪物渐增。仓楹斲桷之制。灿然而毕备。斋楼庖副之所。秩然而有序。笾豆牲醴于斯。揖让兴俯于斯。吾党之士庶几有所瞻依。而羹于食而墙于立矣。天道有显晦之几。王政有损益之宜。不幸庚午毁籍。遍及本院。神板既已荒原矣。栋宇亦已墟莽矣。但见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则远迩襟绅之行过洞门者。顾安得三遇如常。而不为之彷徨怵惕也哉。后二十馀年乙未。一方人士。因彝衷之所同。即其旧址而更谋数间屋子。上而不僭于邦制。下而少伸于舆情。始于六月某甲。讫于九月某甲。堂室凡若干楹。库厨凡若干架。得日凡四阅朔。盖士林与本孙之诚力。可谓两尽而无馀矣。虽然盖闻尊卫之道。不在于祠宇崇奉。而在乎读其书讲其道。今距二先生之世远矣。杞宋虽无徵。而 国朝清白吏之案。西厓先生永慕之编。班班可据。不可曰寂寥。则幸使诸君子之居于是邦者。因其所可据而想其所无徵。体先生之心法。尚先生之风节。清白以持其身。忠直以事其君。益自砥砺。如恐不及。则是乃所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8H 页
 谓不报之报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诸君盍相与勉之哉。先生之裔孙金炳昊,玉离焕等。与士人柳璧镐实掌其事。将以某月日落之。责不佞识其颠末。不佞亦忝在堂任。义不敢辞。遂书之如此云尔。
谓不报之报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诸君盍相与勉之哉。先生之裔孙金炳昊,玉离焕等。与士人柳璧镐实掌其事。将以某月日落之。责不佞识其颠末。不佞亦忝在堂任。义不敢辞。遂书之如此云尔。鉴湖堂重修记
堂在桼谷梅湖之上。李石潭先生晚年琴书之所也。傍有一条短瀑。炯然若飞镜。其南断岸数十尺。又有数三疏松。偃謇苍郁。隐然有岁寒之期。皆可观也。公尝乐于斯。游息于斯。规置数架。而扁之曰鉴湖之堂。因命季子鉴湖公嗣守之。家庭付授之意。夫岂偶然而已哉。自是公日处其中。读书讲道。勉其所以不坠先训。而远迩翕然推之为鉴湖主人。噫方是时也。公之两侄历扬清显。金貂耀门。而公独以盛满为戒。清慎自持。视浮云于轩驷。附馀日于坟籍。以是人处是堂而无愧。以是堂得主人而愈高。则公之所以附畀于当日者。安得不以仲默为归耶。呜呼悕矣。堂岁久颓弊。中间缮治者再。而居然之间。历年又多。昔之整顿者。或至于欹仄。向之完美者。或至于缺坏。则后嗣子孙之情。又安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8L 页
 得三遇如常。而不思所以改葺之道乎。乃者后孙某某等。相与诹度。相与拮据。于以复旧日之规模。葆先祖之遗躅。而欹仄者于是而复正。缺坏者于是而复完。不亦美哉。工既告讫。使其族子相河甫跋涉数百里。徵记于余。余非其人也。既屡辞而不获。则窃慕朱夫子记述冰玉堂之故事。遂不揆而为之记。
得三遇如常。而不思所以改葺之道乎。乃者后孙某某等。相与诹度。相与拮据。于以复旧日之规模。葆先祖之遗躅。而欹仄者于是而复正。缺坏者于是而复完。不亦美哉。工既告讫。使其族子相河甫跋涉数百里。徵记于余。余非其人也。既屡辞而不获。则窃慕朱夫子记述冰玉堂之故事。遂不揆而为之记。兰皋亭记
有地焉。枕腾云之坡。控大海之曲。其势奥如也。其望旷如也。非有风节之卓荦。学识之渊邃者。何以称焉。此南氏兰皋亭之所以移筑也。公之后孙启焕朝曮等。驰书数百里。徵记于不佞。不佞窃惟诸公此举。非直为景物役也。盖亦想像寓慕于兰皋翁之髣髴者乎。噫先生以卓异之姿。袭义方之教。自读孝经。日用服习。不越乎忠孝二字耳。是以居家则一意承顺。忠养备极。惟恐一毫之或咈。及值岛夷之乱则公以弱冠赴义。慨然有出万死不顾一生之志。而投书郭红衣幕下。备糗粮峙器械。以为制挺鞭橽(鞭挞)之策。其志尽大矣。其规模尽密矣。虽古所称金城方略。何以加焉。常好读古人书。研精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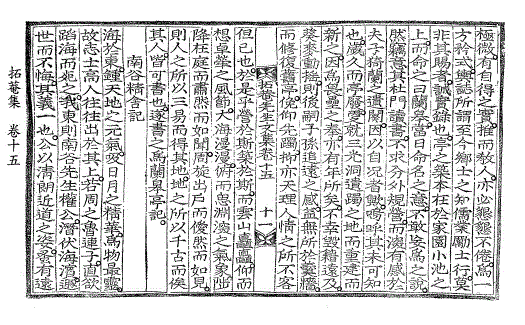 极微。有自得之实。推而教人。亦必恳恳不倦。为一方矜式。舆志所谓至今乡士之知儒业励士行。莫非其赐者。诚实录也。亭之筑本在于家园小池之上。而命之曰兰皋。当日命名之意。不敢妄为之说。然窃意其杜门读书。不求分外规营。而深有感于夫子猗兰之遗阕。因以自况者欤。呜呼其未可知也。岁久而亭废。更就三光洞遗躅之地而重建而新之。因为畏垒之奉。亦有年所矣。不幸毁籍远及。葵麦动摇。则后嗣子孙追远之感。益无所于羹墙。而修复旧亭。俛仰先躅。抑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客但已也。于是乎营于斯筑于斯。而云山矗矗。仰而想卓荦之风节。大海漫漫。俯而思渊深之气象。陟降在庭而肃然而如闻。周旋出户而僾然而如见。则人之所以三易而得其地。地之所以千古而俟其人。皆可书也。遂书之为兰皋亭记。
极微。有自得之实。推而教人。亦必恳恳不倦。为一方矜式。舆志所谓至今乡士之知儒业励士行。莫非其赐者。诚实录也。亭之筑本在于家园小池之上。而命之曰兰皋。当日命名之意。不敢妄为之说。然窃意其杜门读书。不求分外规营。而深有感于夫子猗兰之遗阕。因以自况者欤。呜呼其未可知也。岁久而亭废。更就三光洞遗躅之地而重建而新之。因为畏垒之奉。亦有年所矣。不幸毁籍远及。葵麦动摇。则后嗣子孙追远之感。益无所于羹墙。而修复旧亭。俛仰先躅。抑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客但已也。于是乎营于斯筑于斯。而云山矗矗。仰而想卓荦之风节。大海漫漫。俯而思渊深之气象。陟降在庭而肃然而如闻。周旋出户而僾然而如见。则人之所以三易而得其地。地之所以千古而俟其人。皆可书也。遂书之为兰皋亭记。南谷精舍记
海于东。钟天地之元气。吸日月之精华。为物最灵。故志士高人往往出于其上。若周之鲁连子。直欲蹈海而死之。我东则南谷先生权公。潜伏海滨。遁世而不悔。其义一也。公以清朗近道之姿。蚤有远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9L 页
 大之识。尝寓慕于朱夫子远游之篇。次其韵而矢其志。所以自期者。已不浅矣。逮至柔兆之变。和议横流。甘受帝秦之辱。而公以一介国子生。抗疏天门。敢言不讳。请斩主和之臣以谢天下。而其辞旨凛然。足以有辞于万世矣。是以桐溪先生一见称赏曰此真扶天下之纲常。吾心可与此子说。公读桐溪先生山城劄子。亦曰祖宗三百年元气。养得堂堂第一流。是其一片忠赤。默契于言意之表。而一区南谷。即桐溪之某里耳。此岂一时慷慨之士所能及哉。噫公尝于晚岁。以近里二字颜其室。又作箴而自警。六十年鞭辟向里之功。孳孳不懈。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故其大节树立。确然若砥柱。有本者固如是矣。学问之力。焉可诬也。呜呼。公既殁。沧桑屡嬗。当日盘旋之谷。翳然而墟莽。此则气数之适然。而人事之变。亦从而系之。故后嗣诸孙。因公菟裘之计。遂迁居于英山之新谷。盖述先志也。往岁辛丑。嗣孙孝达等。重建近里斋。为墙羹瞻依之所。而复以南谷书堂四字扁其堂。即濂溪夫子不忘乡关之意也。既落之三年癸卯。后孙翰模甫问记于余。余非其人也。既屡辞而不获。则因复之
大之识。尝寓慕于朱夫子远游之篇。次其韵而矢其志。所以自期者。已不浅矣。逮至柔兆之变。和议横流。甘受帝秦之辱。而公以一介国子生。抗疏天门。敢言不讳。请斩主和之臣以谢天下。而其辞旨凛然。足以有辞于万世矣。是以桐溪先生一见称赏曰此真扶天下之纲常。吾心可与此子说。公读桐溪先生山城劄子。亦曰祖宗三百年元气。养得堂堂第一流。是其一片忠赤。默契于言意之表。而一区南谷。即桐溪之某里耳。此岂一时慷慨之士所能及哉。噫公尝于晚岁。以近里二字颜其室。又作箴而自警。六十年鞭辟向里之功。孳孳不懈。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故其大节树立。确然若砥柱。有本者固如是矣。学问之力。焉可诬也。呜呼。公既殁。沧桑屡嬗。当日盘旋之谷。翳然而墟莽。此则气数之适然。而人事之变。亦从而系之。故后嗣诸孙。因公菟裘之计。遂迁居于英山之新谷。盖述先志也。往岁辛丑。嗣孙孝达等。重建近里斋。为墙羹瞻依之所。而复以南谷书堂四字扁其堂。即濂溪夫子不忘乡关之意也。既落之三年癸卯。后孙翰模甫问记于余。余非其人也。既屡辞而不获。则因复之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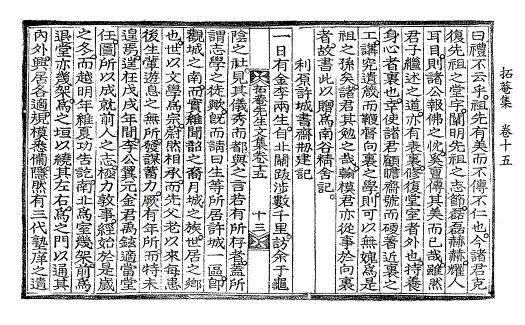 曰礼不云乎。祖先有美而不传不仁也。今诸君克复先祖之堂宇。阐明先祖之志节。磊磊赫赫。耀人耳目。则诸公报佛之忱。奚亶传其美而已哉。虽然君子继述之道。亦有表里。修复堂室者外也。持养身心者里也。幸使诸君顾瞻斋号而硬著近里之工。讲究遗箴而鞭督向里之学。则可以无愧为是祖之孙矣。诸君其勉之哉。翰模君亦从事于向里者。故书此以赠为南谷精舍记。
曰礼不云乎。祖先有美而不传不仁也。今诸君克复先祖之堂宇。阐明先祖之志节。磊磊赫赫。耀人耳目。则诸公报佛之忱。奚亶传其美而已哉。虽然君子继述之道。亦有表里。修复堂室者外也。持养身心者里也。幸使诸君顾瞻斋号而硬著近里之工。讲究遗箴而鞭督向里之学。则可以无愧为是祖之孙矣。诸君其勉之哉。翰模君亦从事于向里者。故书此以赠为南谷精舍记。利原许城书斋刱建记
一日有金李两生。自北关跋涉数千里。访余于龟阴之社。见其仪秀而都。与之言若有所存者。盖所谓志学之徒欤。既而请曰生等所居许城一区。即观城之南。而实维闻韶之裔月城之族。世居之乡也。世以文学为宗。蔚然相承。而先父老以来每患后生辈游息之无所。发谋蓄力。厥有年所。而特未遑焉。𨓏在戊戌年间。李公翼元,金君禹铉适当堂任。图所以成就前人之志。极力敦事。经始于是岁之冬。而越明年维夏功告讫。南北为室几架。前为退堂亦几架。为之垣以绕其左右。为之门以通其内外。兴居各适。规模悉备。隐然有三代塾庠之遗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0L 页
 制。使一方之士。不患抱坟策而靡所归。则玆岂非吾夫子所称百工之肆者乎。夫如是则斋固不可以无其名。亦不可以无记事之文。玆庸仰溷于下执事。惟丈人图之。余作而叹曰不亦善乎。成人之美。君子所乐为也。余虽耄荒敢辞诸。请以平日所闻于父师者。为诸君诵之。因以命之名可乎。子思子著思诚之目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夫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也。故程夫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请取此而名之曰五之之斋。又取学记相观善之言。谓其堂曰观善。又取朱夫子进学不已之训。谓其门曰进学。噫师之所以为教。弟子之所以为学。大抵皆不外乎是也。傥使诸君顾名思义。入门而思如何而为进学。升堂而思如何而为观善。处于斋则思所以学之问之思之辨之以致其知。而既知之。又必力行之。勉勉循循。不得弗措。覆一篑而进于山。掘九仞而及于泉。则将见半亩儒宫。俨然为兴学作人之基本。而楣上题额。得免涴墨之讥矣。可不勉哉。抑又有一说。北关距京师千里之远。其人瞀瞀几乎莫知其所之。而 圣祖龙兴。
制。使一方之士。不患抱坟策而靡所归。则玆岂非吾夫子所称百工之肆者乎。夫如是则斋固不可以无其名。亦不可以无记事之文。玆庸仰溷于下执事。惟丈人图之。余作而叹曰不亦善乎。成人之美。君子所乐为也。余虽耄荒敢辞诸。请以平日所闻于父师者。为诸君诵之。因以命之名可乎。子思子著思诚之目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夫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也。故程夫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请取此而名之曰五之之斋。又取学记相观善之言。谓其堂曰观善。又取朱夫子进学不已之训。谓其门曰进学。噫师之所以为教。弟子之所以为学。大抵皆不外乎是也。傥使诸君顾名思义。入门而思如何而为进学。升堂而思如何而为观善。处于斋则思所以学之问之思之辨之以致其知。而既知之。又必力行之。勉勉循循。不得弗措。覆一篑而进于山。掘九仞而及于泉。则将见半亩儒宫。俨然为兴学作人之基本。而楣上题额。得免涴墨之讥矣。可不勉哉。抑又有一说。北关距京师千里之远。其人瞀瞀几乎莫知其所之。而 圣祖龙兴。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1H 页
 列圣继作。上下五百年之閒。风俗与化移易。开书塾于往往。蔼弦诵于家家。则 圣朝鸢鱼之化。于是为盛。而诸君所以应时而兴起者。抑亦皞皞而不知为之者欤。更愿诸君益思自励。歌咏先王。以效尘刹之报。则是区区之望也。李生名英寅。即翼元之免孙。金生名秉燮。为禹铉之从子云。
列圣继作。上下五百年之閒。风俗与化移易。开书塾于往往。蔼弦诵于家家。则 圣朝鸢鱼之化。于是为盛。而诸君所以应时而兴起者。抑亦皞皞而不知为之者欤。更愿诸君益思自励。歌咏先王。以效尘刹之报。则是区区之望也。李生名英寅。即翼元之免孙。金生名秉燮。为禹铉之从子云。观澜亭重建记
岭之晋阳。为山水佳处。而清淑之所郁积也。万历以来。硕人君子之治亭榭占形胜。蔚然而相望。若故赠小司马许公国柱观澜之亭。亦其一也。亭在防御山下濂沧之上。尽得清淑之尤者。夫濂江之水。发源于智异山。萦洄曲折。遇山而滀。一鉴前开。万状毕露。防之为山。巅崖崛嵂。林壑幽深。临水而停。壁立千仞。云屏如画。其天作地生之状。类智者之所施设。非有倜傥雄伟之节。恬旷雅洁之怀。则莫得以称焉。时则许公以忠勇不群之才。值龙蛇菲茹之难。奋身先唱。七百影从。遂使凶锋摧折。屹然为江淮之保障。而大贤之褒启郑重。 圣朝之鉴临如烛。录三等之勋。升御侮之秩。功烈其盛矣。望实其隆矣。惟其恬退不伐之性。独以大树为归。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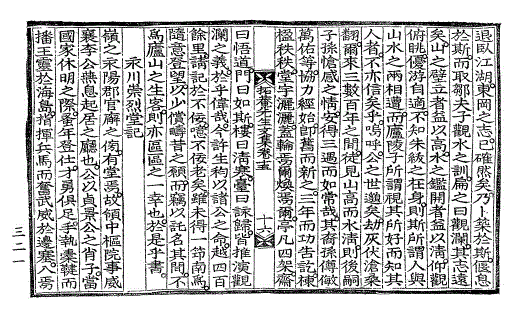 退卧江湖。东冈之志。已确然矣。乃卜筑于斯。偃息于斯。而取邹夫子观水之训。扁之曰观澜。其志远矣。山之壁立者益以高。水之鉴开者益以清。仰观俯眺。优游自适。不知朱绂之在身。则斯所谓人与山水之两相遭。而庐陵子所谓视其所好而知其人者。不亦信矣乎。呜呼。公之世邈矣。劫灰伏沧桑翻。尔来三数百年之间。徒见山高而水清。则后嗣子孙怆感之情。安得三遇而如常哉。其裔孙僔
退卧江湖。东冈之志。已确然矣。乃卜筑于斯。偃息于斯。而取邹夫子观水之训。扁之曰观澜。其志远矣。山之壁立者益以高。水之鉴开者益以清。仰观俯眺。优游自适。不知朱绂之在身。则斯所谓人与山水之两相遭。而庐陵子所谓视其所好而知其人者。不亦信矣乎。呜呼。公之世邈矣。劫灰伏沧桑翻。尔来三数百年之间。徒见山高而水清。则后嗣子孙怆感之情。安得三遇而如常哉。其裔孙僔永川崇烈堂记
岭之永阳郡官廨之傍。有堂焉。故领中枢院事威襄李公燕息起居之厅也。公以贞景公之肖子。当国家休明之际。蚤年登仕。才勇俱足。手执橐鞬而播王灵于海岛。指挥兵马而奋武威于边塞。入焉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2H 页
 而有博陆之风采。出焉而为江淮之保障。 圣明设宴以劳之。 储宫执爵以宠之。是其勋名之震耀。宠赉之便蕃。可谓前古所罕。而唐史所称功盖一世而主不疑者非欤。方其建节南下。昼锦之荣。溢于乡里。而公之治颖之志。于是而得。遂拓开于斯。营筑于斯。为寝为廊而内外之制辨矣。为室为堂而暄凉之候适矣。天之所以眷佑善人。宜使之永锡祚胤。绳绳勿替。而惟其气数有缺齾。物理有倾覆。召伯之祀既已忽诸。而魏公之宅居然易主。则吾南人士遇墟之感。岂亶为葵麦动摇之叹而已哉。往者永之父老前辈。衋然追想。议奉神栖以寓墙羹之慕。盖所谓义起之礼也。乃者公之傍裔李殷和甫。与廷华台秀。互相咨度。既复公之堂室庭宇。又还公之土田臧获。而三数百载之下。光景昭回。遗躅宛然。意者公之英灵毅魄。陟降于庭。而悦豫于无穷矣。于乎伟哉。堂固不可以无名矣。既又命之曰崇烈之堂。因属余而记之。余作而叹曰有是哉。天之记善不忘。愈久而愈不可诬者欤。是堂之既成而旋易。既废而且复。俱非人力之可为。而有关于时运盛衰。则愚未知百岁之下。复有如
而有博陆之风采。出焉而为江淮之保障。 圣明设宴以劳之。 储宫执爵以宠之。是其勋名之震耀。宠赉之便蕃。可谓前古所罕。而唐史所称功盖一世而主不疑者非欤。方其建节南下。昼锦之荣。溢于乡里。而公之治颖之志。于是而得。遂拓开于斯。营筑于斯。为寝为廊而内外之制辨矣。为室为堂而暄凉之候适矣。天之所以眷佑善人。宜使之永锡祚胤。绳绳勿替。而惟其气数有缺齾。物理有倾覆。召伯之祀既已忽诸。而魏公之宅居然易主。则吾南人士遇墟之感。岂亶为葵麦动摇之叹而已哉。往者永之父老前辈。衋然追想。议奉神栖以寓墙羹之慕。盖所谓义起之礼也。乃者公之傍裔李殷和甫。与廷华台秀。互相咨度。既复公之堂室庭宇。又还公之土田臧获。而三数百载之下。光景昭回。遗躅宛然。意者公之英灵毅魄。陟降于庭。而悦豫于无穷矣。于乎伟哉。堂固不可以无名矣。既又命之曰崇烈之堂。因属余而记之。余作而叹曰有是哉。天之记善不忘。愈久而愈不可诬者欤。是堂之既成而旋易。既废而且复。俱非人力之可为。而有关于时运盛衰。则愚未知百岁之下。复有如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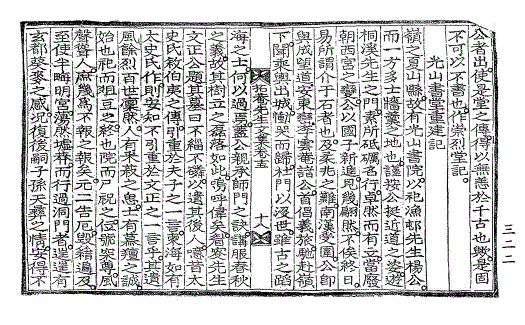 公者出。使是堂之传。得以无恙于千古也欤。是固不可以不书也。作崇烈堂记。
公者出。使是堂之传。得以无恙于千古也欤。是固不可以不书也。作崇烈堂记。光山书堂重建记
岭之夏山县。故有光山书院。以祀渔村先生杨公。而一方多士墙羹之地也。谨按公挺近道之姿。游桐溪先生之门。素所砥砺名行。卓然而有立。当废朝西宫之变。公以国子新进。见几翩然。不俟终日。易所谓介于石者也。及柔兆之难。南汉受围。公即与成望道,安东峦,李云庵诸公。首倡义旅。驰赴岭下。闻乘舆出城。恸哭而归。杜门以没世。虽古之蹈海之士。何以过焉。盖公亲承师门之诀。讲服春秋之义。故其树立之磊落如此。呜呼伟矣。眉叟先生文正公题其墓曰不缁不磷。以遗其后人。噫昔太史氏叙伯夷之传。引重于夫子之一言。东海如有太史氏作。则安知不引重于文正之一言乎。其遗风馀烈百世凛然。人有采菽之思。士有慕膻之诚。始也祀而俎豆之。终也院而尸祝之。位号深尊。风声耸人。庶几为不报之报矣。元二告厄。毁籍遍及。至使半亩明宫。荡然墟莽。而行过洞门者。𨓏𨓏有玄都葵麦之感。况复后嗣子孙天彝之情。安得不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3H 页
 惕然而感伤。衋然而彷徨也哉。于是聚首咨度。竭诚规画。以八世孙典焕总其事。又以八世孙淙焕九世孙定奎管其役。乃移占于渔村之西梨冈之下。左右为室三架。西北为堂二架。前为曲楼及退厅合五架。始于某年某日。讫于某年某日。前后费日若干。细大经用亦若干。而大抵竭诸孙之力也。既又施之以旧号曰光山书堂。后孙粲奎等跋涉数百馀里。属余记其事。余作而曰先生之卓节懿行。天壤与存。固无待于后世之寓慕尊尚。然常人之情。远则易于忘。忘则易于废坠。今诸公之修复堂宇。出入瞻仰。盖所谓乐所生而不忘本者也。不亦善乎。请因此而思其所以进于此者。益读先祖之遗书。克体先祖之遗志。办义利于一剑。轻死生于鸿毛。生为名节之士。死为忠义之鬼。则不亶光山之堂。益彰于世。而抑亦有光于先生也。诸公其勉之哉。是为记。
惕然而感伤。衋然而彷徨也哉。于是聚首咨度。竭诚规画。以八世孙典焕总其事。又以八世孙淙焕九世孙定奎管其役。乃移占于渔村之西梨冈之下。左右为室三架。西北为堂二架。前为曲楼及退厅合五架。始于某年某日。讫于某年某日。前后费日若干。细大经用亦若干。而大抵竭诸孙之力也。既又施之以旧号曰光山书堂。后孙粲奎等跋涉数百馀里。属余记其事。余作而曰先生之卓节懿行。天壤与存。固无待于后世之寓慕尊尚。然常人之情。远则易于忘。忘则易于废坠。今诸公之修复堂宇。出入瞻仰。盖所谓乐所生而不忘本者也。不亦善乎。请因此而思其所以进于此者。益读先祖之遗书。克体先祖之遗志。办义利于一剑。轻死生于鸿毛。生为名节之士。死为忠义之鬼。则不亶光山之堂。益彰于世。而抑亦有光于先生也。诸公其勉之哉。是为记。赠参判尹公,参赞尹公神道碑阁记。
近故赠兵曹参判行晋州牧使尹公讳铎字声远。行议政府右参赞尹公讳铣字泽远。皆坡平之出而从父兄弟也。按参判公。以卓荦之才冠绝之勇。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3L 页
 当龙蛇菲茹之乱。奋然先倡。义气横苍。始则驰赴于郭忠翼公幕下。而画赞机筹。举足冲突。屡致剋获之功。既而从文忠金先生于晋阳之围。一发孤城。挺身捍御。而北向稽首。阳阳就死。马革裹还之志。于是而得遂。则太史公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其斯之谓乎。至若参赞公。又废朝全节之臣也。方北党煽乱。西宫废锢。而天理或几乎熄矣。公于是时。乃能进供于锢宫之下。而不慑雷霆。抗言于丛镝之中。而不避机阱。内而尽狄梁公之忠。外而效宁武子之愚。则其所以周旋终始。矢死不变。不亦君子之所难者欤。曹晦谷平勃安刘之一言。可谓深知其志者矣。呜呼。今距两公之世。数三百岁之远矣。而羡道丽牲之石。屹然并峙于其乡。同为一阁而覆之。盖二公事行。虽似不同。而其捐生报国之忠。抗义守正之节。实出于同堂讲确之馀。而义理无二致也。后人之瞻仰并尊。安得不愈久而愈不已哉。然则诸葛武侯成都之碑。羊叔子岘山之石。不必多让也。呜呼伟哉。日公之后孙炳谟君。跋涉四百里而来。徵记于不佞。顾不佞非能言者。而就读二公遗状。窃不胜旷世执鞭之愿。遂略掇其
当龙蛇菲茹之乱。奋然先倡。义气横苍。始则驰赴于郭忠翼公幕下。而画赞机筹。举足冲突。屡致剋获之功。既而从文忠金先生于晋阳之围。一发孤城。挺身捍御。而北向稽首。阳阳就死。马革裹还之志。于是而得遂。则太史公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其斯之谓乎。至若参赞公。又废朝全节之臣也。方北党煽乱。西宫废锢。而天理或几乎熄矣。公于是时。乃能进供于锢宫之下。而不慑雷霆。抗言于丛镝之中。而不避机阱。内而尽狄梁公之忠。外而效宁武子之愚。则其所以周旋终始。矢死不变。不亦君子之所难者欤。曹晦谷平勃安刘之一言。可谓深知其志者矣。呜呼。今距两公之世。数三百岁之远矣。而羡道丽牲之石。屹然并峙于其乡。同为一阁而覆之。盖二公事行。虽似不同。而其捐生报国之忠。抗义守正之节。实出于同堂讲确之馀。而义理无二致也。后人之瞻仰并尊。安得不愈久而愈不已哉。然则诸葛武侯成都之碑。羊叔子岘山之石。不必多让也。呜呼伟哉。日公之后孙炳谟君。跋涉四百里而来。徵记于不佞。顾不佞非能言者。而就读二公遗状。窃不胜旷世执鞭之愿。遂略掇其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4H 页
 槩。并叙其所感如此以为记。
槩。并叙其所感如此以为记。嘉礼洞天记
直宜春之治西数里所有所谓嘉礼洞者。山水佳绝。洞壑清幽。隐然为三十六洞天之一。而许氏得以世居之。盖许氏之先湖隐公。当丽季以直道被黜。迁于峤南之铁城。而后孙上舍公元辅又自铁城移卜于此。为子孙菟裘之基。盖取地胜之可爱也。我退陶先生于公为馆甥。往来栖息。盖有年所矣。尝于玩赏之馀。犁然得仁义之趣。特以大笔手书嘉礼洞天四大字于岩石上。又书书岩二字于其傍。表揭山门。左右交映。山岳为之献贺。草木为之腾彩。直与西序之弘璧。南国之甘棠。并美于千载之下。吾党衿绅之所以仰高山之兴云。咏中原之采菽。庸有极乎。况许氏诸公。以二祖遗孙。缅想当日气象。而愀然若复见者哉。于乎悕矣。往者建祠德谷。春秋荐祼。庶几羹墙之有地。而运值元二。庙皃遂墟。往往葵麦之感。不能三遇而如常。则未知诸君子于此。将何以报佛于无穷也。许氏一门询谋于本乡士林。为洞天修契之事。而列书姓名。各出物力。绍馀韵于既往。葆贤躅于方来。则其卫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4L 页
 道尊贤之功。亦足以有辞于吾林矣。其可已乎。不佞以藐然末学。亦尝敬慕先生之风。北入陶山。祇拜尚德之庙。历登岩栖之轩。愿为浴沂之童子而不可得矣。今者许君■(禾匀)模等。乃以洞天记事嘱余。噫莫非先生之役也。窃以托名为荣。遂不辞而略叙颠末。以备洞天故事云尔。
道尊贤之功。亦足以有辞于吾林矣。其可已乎。不佞以藐然末学。亦尝敬慕先生之风。北入陶山。祇拜尚德之庙。历登岩栖之轩。愿为浴沂之童子而不可得矣。今者许君■(禾匀)模等。乃以洞天记事嘱余。噫莫非先生之役也。窃以托名为荣。遂不辞而略叙颠末。以备洞天故事云尔。资宪大夫礼曹判书朴公墓坛碑阴记
东都王城南一舍之地。有九旺洞桃花谷者。国初资宪大夫礼曹判书咸阳朴公冠舄之藏也。公位跻上卿。名显一代。羡道仪物之饰。法无不具。而今距五百有馀岁矣。沧桑翻劫火伏。羊叔子岘山之石。剥落而无传。范明友冢中之奴。更不得出来。则正大夫陟降之灵。安知不徘徊而叹息乎。惟是桃花谷之形局。昭载于世传之山图。判书嶝之名称。播传于舆氓之口碑。且夫自公以下五六世邱垄。次第成行。俨然为欧阳氏之泷冈。则不待西人之深目。而此足为千古之的證也。虽然公之配位贞夫人兆域。亦在同原。而尊卑之序。上下之次。有不得以悬揣者。与其赍疑而未定。孰若设坛而合享之为愈乎。于是后孙某某等。聚首询谋。刱设坛壝。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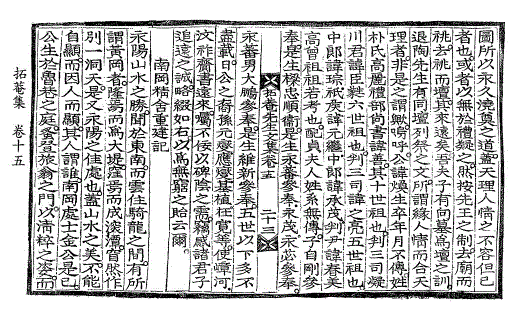 图所以永久浇奠之道。盖天理人情之不容但已者也。或者以无于礼疑之。然按先王之制。去庙而祧。去祧而坛。其来远矣。吾夫子有向墓为坛之训。退陶先生有同坛列祭之文。所谓缘人情而合天理者。非是之谓欤。呜呼。公讳焕生卒年月不传。姓朴氏高丽礼部尚书讳善。其十世祖也。判三司凝川君讳臣蕤六世祖也。判三司讳之亮五世祖也。中郎讳琮,祇侯讳元继,中郎讳承茂,判尹讳春美高曾祖祖若考也。配贞夫人姓系无传。子自刚参奉。是生梁忠顺卫。是生永蕃参奉,永茂,永苾参奉。永蕃男大鹏参奉。是生维新参奉。五世以下多不尽载。日公之裔孙元燮,应燮,基植,在宽等。使嶂河,汶祚赍书远来。嘱不佞以碑阴之需。窃感诸君子追远之诚。略缀如右。以为无穷之贻云尔。
图所以永久浇奠之道。盖天理人情之不容但已者也。或者以无于礼疑之。然按先王之制。去庙而祧。去祧而坛。其来远矣。吾夫子有向墓为坛之训。退陶先生有同坛列祭之文。所谓缘人情而合天理者。非是之谓欤。呜呼。公讳焕生卒年月不传。姓朴氏高丽礼部尚书讳善。其十世祖也。判三司凝川君讳臣蕤六世祖也。判三司讳之亮五世祖也。中郎讳琮,祇侯讳元继,中郎讳承茂,判尹讳春美高曾祖祖若考也。配贞夫人姓系无传。子自刚参奉。是生梁忠顺卫。是生永蕃参奉,永茂,永苾参奉。永蕃男大鹏参奉。是生维新参奉。五世以下多不尽载。日公之裔孙元燮,应燮,基植,在宽等。使嶂河,汶祚赍书远来。嘱不佞以碑阴之需。窃感诸君子追远之诚。略缀如右。以为无穷之贻云尔。南冈精舍重建记
永阳山水之胜。闻于东南。而云住骑龙之间。有所谓黄冈者。隆焉而为大堤。洼焉而成深潭。窅然作别一洞天。是又永阳之佳处也。盖山水之美。不能自显。而因人而显。其人谓谁。南冈处士金公是已。公生于鲁巷之庭。蚤登旅翁之门。以清粹之姿。而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5L 页
 加之以勤笃之工。以聪颖之才。而袭之以磨砻之力。所懋者日用常行也。所讲者师门旨诀也。择地而蹈。好古而敏。所以治心修身而施于家者。抑莫非大贤垆韛中出来者欤。岁值龙蛇。旋遭先公之殉国。拚柏悲号之馀。泊然无意于世。退处黄冈。缚得数椽。命之曰南冈精舍。盖为晚暮琴书之托。子弟藏修之所。而视一切声利如浮云也。不幸沧桑屡翻。堂室遂墟。行过洞门。辄不胜葵麦动摇之感。至 今上辛丑。后孙俊熙等。衋然于斯。聚首咨度。发虑规划。乃移卜于大堤之上。而筑石而完其缺。引水而规其中。遂建八架精舍。管取临对之胜。东西燠室四架。中间凉轩亦四架。增廓当日之规模。挽回百年之光华。子孙肯构之诚。于是至矣。功既告讫。使其堂弟相熙问记于余。余作而曰不亦善乎。礼曰礼不忘其本。乐乐其所自生。而不忘本矣。君子继述之道。有大于是者。以孝悌忠信为基址。以诗书礼乐为间架。入而栋梁于家乡。出而藩屏于王国。则南冈翁在天之灵。安得不悦豫于无穷乎。然则一区精舍之轮焉焕焉者。不过为瞻依寓慕之一助耳。诸君以为如何也。
加之以勤笃之工。以聪颖之才。而袭之以磨砻之力。所懋者日用常行也。所讲者师门旨诀也。择地而蹈。好古而敏。所以治心修身而施于家者。抑莫非大贤垆韛中出来者欤。岁值龙蛇。旋遭先公之殉国。拚柏悲号之馀。泊然无意于世。退处黄冈。缚得数椽。命之曰南冈精舍。盖为晚暮琴书之托。子弟藏修之所。而视一切声利如浮云也。不幸沧桑屡翻。堂室遂墟。行过洞门。辄不胜葵麦动摇之感。至 今上辛丑。后孙俊熙等。衋然于斯。聚首咨度。发虑规划。乃移卜于大堤之上。而筑石而完其缺。引水而规其中。遂建八架精舍。管取临对之胜。东西燠室四架。中间凉轩亦四架。增廓当日之规模。挽回百年之光华。子孙肯构之诚。于是至矣。功既告讫。使其堂弟相熙问记于余。余作而曰不亦善乎。礼曰礼不忘其本。乐乐其所自生。而不忘本矣。君子继述之道。有大于是者。以孝悌忠信为基址。以诗书礼乐为间架。入而栋梁于家乡。出而藩屏于王国。则南冈翁在天之灵。安得不悦豫于无穷乎。然则一区精舍之轮焉焕焉者。不过为瞻依寓慕之一助耳。诸君以为如何也。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6H 页
 履露斋记
履露斋记礼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怆之心。如将不及。君子思亲之心。何时不然。而独于雨露之候霜露之节。必如是者何哉。盖当雨露霏霏。百物昭回。则安知祖先之灵。不与之俱回乎。霜露凄凄。百物归藏。则安知祖先之灵。不与之偕藏乎。于是而怵惕者愈深。悽怆者益切。有不能自已者。此许氏诸公履露之斋所以作也。先人之邱垄累然而成列。百世之松杉。菀然而悄茜。春而展省于是则怵惕如见之感。可以少伸矣。秋而祼荐于是。则悽怆如在之慕。可以粗效矣。彼雨露也霜露也。不过为随时触感之时物。而斋者所以寓感于无穷者耳。甄氏燕思之亭。晦翁寒泉之筑。亦岂非为是之故欤。不宁惟是。使子姓昆弟之游息于斯。诵读于斯者。优而柔之。如雨露之滋苗。资而得之。如霜露之成材。上不坠祖宗之绪业。下不失家门之楷范。则是斋之作。永有辞于来世。而抑亦为风教之一助也。不亦伟哉。今因本孙在璨之书请。姑记所闻而归之。若夫室堂之规制。营建之年月。林园玩赏之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6L 页
 趣。自有文士之能言者。今不暇云。
趣。自有文士之能言者。今不暇云。芦溪斋舍重建记
直草溪治东磊方之里。有曰芦溪精舍者。故芦溪安先生隐居讲道之墟也。先生以高迈之姿。尽探索之工。学道于佔𠌫之门。讲劘于寒暄之席。退处江湖。卓然为昭代之逸民。而遗芬剩馥。尚有不泯。则后人之瞻仰想像。不于斯亭而更于何处乎。其刱在弘治戊申。今距三百有馀岁矣。中间废坏。不知几何年。而颜井湮矣。白鹿墟矣。行过洞门每有西林之感。 明陵壬申。一方襟绅。祝公于松原之祠。而又以公之曾孙磊谷公配之。磊翁即龟岩李公之高弟也。孝弟忠义之实。清白雅洁之操。践履之笃。出处之正。有辞于当世。无愧于贤祖。一体齐享。薰蒿无间。尤岂非斯文之盛举而子孙之荣幸也哉。苾芬时升。冠佩坌集。盖秩秩尔跄跄尔。邦人知所敬。学者知所向。而阴阳二厄。今昔之所不免也。毁籍遽及。庙貌遂墟。颓画栋于草莽。奉神板于泉壤。凡行路之人。莫不彷徨而太息。况冠儒而服儒。为昆而为孙者。当作何如痛也。聚首伤叹。居然四十星霜。而未尝一日忘也。乃于乙巳某月日。始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7H 页
 营别祠。以安二先生神栖。既又以为斋宿不可无所也。揖让不可无地也。即其旧亭之址而规置数架之屋。为室凡几间。为堂亦几间。合而扁之曰著存之斋。功既讫。公之后孙鉴坤晚坤等。以其门父兄之命。请记于不佞。不佞作而曰善哉。佥贤继述之诚。可谓肯构而肯堂矣。窃尝闻君子所以善继善述。又有大者焉。今使佥贤志先生之所志。学先生之所学。入而事亲则尽其孝而不懈。出而事君则竭其忠而无隐。以之律身也。祛浮华而敦本实。以之御家也。崇节俭而尚礼让。由内而及外。自迩而推远。则二公在天之灵。陟降庭止。而安得不悦豫于冥冥乎。惟佥君子其勉之哉。是为记。
营别祠。以安二先生神栖。既又以为斋宿不可无所也。揖让不可无地也。即其旧亭之址而规置数架之屋。为室凡几间。为堂亦几间。合而扁之曰著存之斋。功既讫。公之后孙鉴坤晚坤等。以其门父兄之命。请记于不佞。不佞作而曰善哉。佥贤继述之诚。可谓肯构而肯堂矣。窃尝闻君子所以善继善述。又有大者焉。今使佥贤志先生之所志。学先生之所学。入而事亲则尽其孝而不懈。出而事君则竭其忠而无隐。以之律身也。祛浮华而敦本实。以之御家也。崇节俭而尚礼让。由内而及外。自迩而推远。则二公在天之灵。陟降庭止。而安得不悦豫于冥冥乎。惟佥君子其勉之哉。是为记。良昭公影堂重修记
全罗道长城卧谷之里。有数间影阁。为一方人士之所尊慕者。即我族先祖右议政良昭公遗像奉安之所也。谨按公以詹事公之肖孙。姿性敏颖。宇量弘伟。居家孝悌之实。学道淹博之识。蔚然为当世所宗。而家庭气脉之传。有不可诬者矣。逮至 圣朝龙兴。应运而起。抗爽言于 天陛而不忘补衮之责。翊 圣躬于危地而终收带砺之盟。国家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7L 页
 之鸿业得以再造矣。臣子之芹忱可谓粗效矣。于是乎从容赋归。逍遥于孟岩之上。视浮云于轩冕。付馀日于琴书。绿野清谈。未尝一及于平淮之事。则若公者岂非易传所谓介石知退之君子欤。此 圣主所以嗟赏于疏傅之廉退。念轸于九龄之风度。法其形貌。署其名姓。而半幅丹青。高揭 朝堂。以垂无涯之 恩渥。李亨斋所谓进亦荣退亦荣者非耶。既而奉还乡里。立祠揭虔。上以答 列圣之殊渥。下以寓子孙之追慕。而不幸元二告厄。毁籍遍及。鹤林邱墟矣。神栖飘荡矣。行人有葵麦之感。多士切采菽之思。则今玆卧谷之营设。抑亦天理人情之不容但已也。惟其日月滋久。不能无倾仄之患。风雨震陵。不能无腐折之忧。故阖宗咨谋。工匠效力。向日之倾仄者以正。昔日之腐折者以完。轮焉而美焕焉而新。在天洋洋之灵。陟降如在。而孱孙报佛之忱。亦足以有辞于来后。于乎伟哉。范蠡金铸之像。留于越宫。而未闻后人之虔奉。诸葛帛绣之像。传于成都。而未闻百世之共尊。由是观之。则生而荣耀于家国。殁而永寿于千百者。惟公之像为然乎。东冈先生叙之曰揭于朝堂也。
之鸿业得以再造矣。臣子之芹忱可谓粗效矣。于是乎从容赋归。逍遥于孟岩之上。视浮云于轩冕。付馀日于琴书。绿野清谈。未尝一及于平淮之事。则若公者岂非易传所谓介石知退之君子欤。此 圣主所以嗟赏于疏傅之廉退。念轸于九龄之风度。法其形貌。署其名姓。而半幅丹青。高揭 朝堂。以垂无涯之 恩渥。李亨斋所谓进亦荣退亦荣者非耶。既而奉还乡里。立祠揭虔。上以答 列圣之殊渥。下以寓子孙之追慕。而不幸元二告厄。毁籍遍及。鹤林邱墟矣。神栖飘荡矣。行人有葵麦之感。多士切采菽之思。则今玆卧谷之营设。抑亦天理人情之不容但已也。惟其日月滋久。不能无倾仄之患。风雨震陵。不能无腐折之忧。故阖宗咨谋。工匠效力。向日之倾仄者以正。昔日之腐折者以完。轮焉而美焕焉而新。在天洋洋之灵。陟降如在。而孱孙报佛之忱。亦足以有辞于来后。于乎伟哉。范蠡金铸之像。留于越宫。而未闻后人之虔奉。诸葛帛绣之像。传于成都。而未闻百世之共尊。由是观之。则生而荣耀于家国。殁而永寿于千百者。惟公之像为然乎。东冈先生叙之曰揭于朝堂也。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8H 页
 贤良矜式而益勉。在于乡闾也。懦顽闻风而有立。于乎其尽之矣。公之裔孙瓒赫甫跋涉千里。请余记其事。顾道和忝在傍裔之列。不敢以不文辞。遂略志颠末如此。以寓旷世之感慕云尔。
贤良矜式而益勉。在于乡闾也。懦顽闻风而有立。于乎其尽之矣。公之裔孙瓒赫甫跋涉千里。请余记其事。顾道和忝在傍裔之列。不敢以不文辞。遂略志颠末如此。以寓旷世之感慕云尔。寓慕斋记
礼曰礼不忘其本。乐乐其所自生。盖报本乐生。天理之当然。而人心之不容已者也。今权氏寓慕之斋。其亦有得于礼乐之义欤。按权氏之先丹邱公。以太师阀阅之裔。当国家休明之际。文学足以黼黻皇猷。德义足以陶范乡俗。而退然自守。遁世无闷。中间一命。出于朝廷之推毂。而犹不欲舍所好而屈其志焉。浩然归卧于洛江之上。而箪瓢为乐事。花竹为活计。千驷万钟不足以易吾之乐。则若公者岂非所谓畎亩嚣嚣之徒欤。惟其不试于世。故所以内修者益密。书非圣不读。物非义不取。训子弟则必以颜氏之家法。奖后进则必以安定之规模。晦谷先生深叹其诲人不倦。监察柳公亦称其正直不挠。是皆当日公评之不可诬者也。后数百岁。俛庵李公题其墓曰不赢其躬。委祉于后。其遗风远韵之愈久而不泯又可见。公之后嗣子孙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8L 页
 居于山河之里者。衋然有桑梓之感。忾然有墙羹之慕。规置一屋。以为髣髴瞻依之所。而扁之曰寓慕。此孝子慈孙无穷之情也。后孙相璟相奭等。要余记其事。余非能言者。而窃悲其志。因复之曰权氏之所慕者何事。其非祖先孝悌之道乎。其非祖先诗礼之业乎。入则敦行孝悌。以化其家人。出则勉学诗礼。以导其子弟。自身而家。自家而乡。则将见半亩斋阁不亶为寓慕之所。而抑亦有补于国家善俗之方矣。不亦休哉。奭君尝从余游。其志盖不苟也。故记之如右。
居于山河之里者。衋然有桑梓之感。忾然有墙羹之慕。规置一屋。以为髣髴瞻依之所。而扁之曰寓慕。此孝子慈孙无穷之情也。后孙相璟相奭等。要余记其事。余非能言者。而窃悲其志。因复之曰权氏之所慕者何事。其非祖先孝悌之道乎。其非祖先诗礼之业乎。入则敦行孝悌。以化其家人。出则勉学诗礼。以导其子弟。自身而家。自家而乡。则将见半亩斋阁不亶为寓慕之所。而抑亦有补于国家善俗之方矣。不亦休哉。奭君尝从余游。其志盖不苟也。故记之如右。老松亭记
天下之物。莫不向阳而争荣。故洛城之桃李。渭城之杨柳。灼灼焉竞发。濯濯焉并茂者。大抵皆以是也。独有一株孤松。生老于穷山寂寞之墟。斧斤不得侵。风雪不能屈。苍髯白甲。偃蹇高峙。不与众草木为伍。则孔夫子后凋之叹。范鲁公晚翠之咏。夫岂偶然而已哉。国家 庄陵之际。天命有归。草花落而水动摇。则春台万物。何莫非太阳之光辉也。时则赠判书老松亭李先生。有挺特之姿。有不拔之操。尝以太学生。怛然而泣鼎湖之遗弓。慨然而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9H 页
 慕苍梧之归云。陟彼山台。北望拜稽。而炳炳葵藿之忱。愈老而愈劲。则公之托于老松者。盖以岁寒自期。而不屑为向阳之花木者也。是以金枝玉叶。无不尔或承。三世而有文纯公退陶夫子出焉。卓然为百世之楷模。则所谓溉其根而食其实者非欤。东海之月照临其上。而散无边之清影。西山之竹蟠屈其侧。而伴不世之贞节。洒洒乎其遗韵也。亭亭乎其高标也。人与松而同老。松与人而共峙。则愚未知松耶人耶。人即是松而松即是人耶。吾将往问于靖节先生盘桓之下也。
慕苍梧之归云。陟彼山台。北望拜稽。而炳炳葵藿之忱。愈老而愈劲。则公之托于老松者。盖以岁寒自期。而不屑为向阳之花木者也。是以金枝玉叶。无不尔或承。三世而有文纯公退陶夫子出焉。卓然为百世之楷模。则所谓溉其根而食其实者非欤。东海之月照临其上。而散无边之清影。西山之竹蟠屈其侧。而伴不世之贞节。洒洒乎其遗韵也。亭亭乎其高标也。人与松而同老。松与人而共峙。则愚未知松耶人耶。人即是松而松即是人耶。吾将往问于靖节先生盘桓之下也。泥山亭记
葛萝之一支。北迤而南。南折而西。耸拔为鹰峰。椭转为东岭。循峰而渐低。背岭而傍行。宛转坡坨。结为一局。有田数百亩。横纵鳞鳞。即俗所谓泥邱也。或曰厥土惟涂泥。故名以其实。或曰是谷也称冶谷。故取抟埴之义而名之。有小涧随山屈折而来。西北会于川。其溢也悍急而难越。其涸也介然而成路。上下曲折处。往往成小潭。清澈可爱。盖平常中自有妙处者也。先君子衣履之藏。在岭之腰。每余省拜之日。陟降环视。营度已久。而但力诎未遑。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29L 页
 一日少辈三数人。相与咨询。鸠材若干椽。货田若干亩。规置小屋于其中。编茅以覆之。以待栖息。屋凡三间。中一架为堂。取大学首章之旨。名之曰知止。左右为室各一架。左曰拓庵。取先师展拓二字之训也。右曰观斋。取学记相观而善之语也。合而扁之曰泥山精舍。盖因其地名而寓掉尾之义也。虽其形势凡陋。规模草率。而视愚分不亦侈矣乎。噫余之耄愚蔑识。顾何敢与议于仁智之趣哉。特以素性不喜烦聒。年龄又迫迟暮。思所以栖身养病之道。而非荒闲寂寞之滨。则亦不可以谐其志也。且闻陋巷之居。别无形胜。而颜氏乐之。舞雩之坛。只有树木。而点也咏之。向使二子而遇此。则箪瓢之乐。其可改乎。鼓瑟之咏。其可已乎。况复山之平衍。足以休吾之软脚。涧之清冷。足以涤吾之烦襟。又何必理谢公之屐。访庐山之面也哉。于是乎筑土为阶。列植梅菊数本。唤清香于雪月而托晚契于风霜。又穿沼于前。畜鱼儿数种。以观夫天渊活泼之机。则逍遥玩赏之际。乐亦无不在矣。既又携书而入。据梧而吟。或温绎旧读。或反覆新闻。疑则阙倦则休。按辔徐行。刊去枝叶。图所以填补既
一日少辈三数人。相与咨询。鸠材若干椽。货田若干亩。规置小屋于其中。编茅以覆之。以待栖息。屋凡三间。中一架为堂。取大学首章之旨。名之曰知止。左右为室各一架。左曰拓庵。取先师展拓二字之训也。右曰观斋。取学记相观而善之语也。合而扁之曰泥山精舍。盖因其地名而寓掉尾之义也。虽其形势凡陋。规模草率。而视愚分不亦侈矣乎。噫余之耄愚蔑识。顾何敢与议于仁智之趣哉。特以素性不喜烦聒。年龄又迫迟暮。思所以栖身养病之道。而非荒闲寂寞之滨。则亦不可以谐其志也。且闻陋巷之居。别无形胜。而颜氏乐之。舞雩之坛。只有树木。而点也咏之。向使二子而遇此。则箪瓢之乐。其可改乎。鼓瑟之咏。其可已乎。况复山之平衍。足以休吾之软脚。涧之清冷。足以涤吾之烦襟。又何必理谢公之屐。访庐山之面也哉。于是乎筑土为阶。列植梅菊数本。唤清香于雪月而托晚契于风霜。又穿沼于前。畜鱼儿数种。以观夫天渊活泼之机。则逍遥玩赏之际。乐亦无不在矣。既又携书而入。据梧而吟。或温绎旧读。或反覆新闻。疑则阙倦则休。按辔徐行。刊去枝叶。图所以填补既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0H 页
 往之万一。而常恐光阴之不贷。幸而赖天之灵。假我数年。得遂其志愿。则庶可以籍手归拜于地下师友而无所恨矣。愿与同志者勉焉。
往之万一。而常恐光阴之不贷。幸而赖天之灵。假我数年。得遂其志愿。则庶可以籍手归拜于地下师友而无所恨矣。愿与同志者勉焉。多学斋重修记
直新宁治东莽苍之地。有曰骑龙山者。即吾宗金氏世居之地也。旧有多学斋在其傍。为宾朋宴集子孙游息之所。大泽前横。贤山远拱。窅然成一洞天。盖东南之奥区也。斋之刱在于 仁陵之际。而星霜屡嬗。风雨漂挠。不免有葵麦动挠之感。乃者金定洛振浩协谋规画。随力修葺。轮焉尔焕焉尔。君子所谓肯堂构者非欤。虽然堂构者外也末也。幸使诸君叙族于斯。课孙于斯。使闻之者感发而兴起。则亦足为风化之一助矣。荀卿子曰弟子勉学。天不忘也。为诸君诵之。
来庵记
吾友洪君稚颜。自北关千里而来。从余游久矣。每见其意气伟然。见得分明。真可谓可与共学矣。可与适道矣。余固爱之信之。尝因其所居里名来源而命其室曰来庵。又推其义而为之记曰。来之时义远矣。一鉴之塘。如许清净。以其有活源之来也。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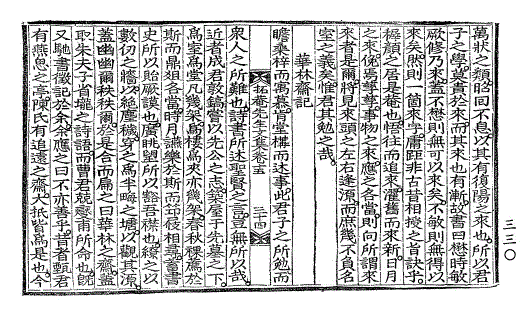 万状之类。昭回不息。以其有复阳之来也。所以君子之学。莫贵于来。而其来也有渐。故书曰懋时敏厥修乃来。盖不懋则无可以来矣。不敏则无得以来矣。然则一个来字。庸距非古昔相授之旨诀乎。稚颜之居是庵也。悟往而追来。濯旧而来新。日月之来。俛焉孳孳。事物之来。应之各当。则向所谓来来者是尔。将见来头之左右逢源。而庶几不负名室之义矣。惟君其勉之哉。
万状之类。昭回不息。以其有复阳之来也。所以君子之学。莫贵于来。而其来也有渐。故书曰懋时敏厥修乃来。盖不懋则无可以来矣。不敏则无得以来矣。然则一个来字。庸距非古昔相授之旨诀乎。稚颜之居是庵也。悟往而追来。濯旧而来新。日月之来。俛焉孳孳。事物之来。应之各当。则向所谓来来者是尔。将见来头之左右逢源。而庶几不负名室之义矣。惟君其勉之哉。华林斋记
瞻桑梓而寓慕。肯堂构而述事。此君子之所勉。而众人之所难也。诗书所述圣贤之言。岂无所以哉。近者成君敦镐尝以先公之志。筑屋于先墓之下。为室为堂凡几架。为楼为夹亦几架。春秋祼荐于斯而鼎俎各当。时月宴乐于斯而筇屐相寻。蓄书史所以贻厥谟也。广眺望所以豁吾襟也。缭之以数仞之墙。以绝尘秽。穿之为半亩之塘。以观其源。盖幽幽尔秩秩尔。于是合而扁之曰华林之斋。盖取朱夫子省垄之诗语。而曹君兢燮甫所命也。既又驰书徵记于余。余应之曰不亦善乎。昔者甄君有燕思之亭。陈氏有追远之斋。大抵皆为是也。今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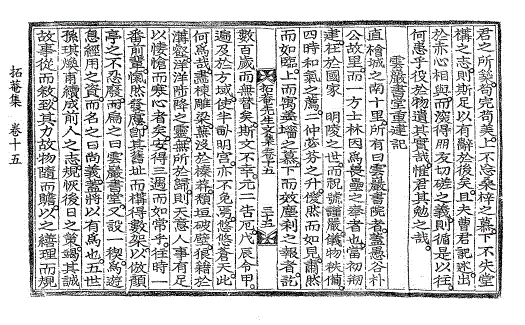 君之所筑。苟完苟美。上不忘桑梓之慕。下不失堂构之志。则斯足以有辞于后矣。且夫曹君记述。出于赤心相与。而深得朋友切磋之义。则循是以往。何患乎役于物遗其实哉。惟君其勉之哉。
君之所筑。苟完苟美。上不忘桑梓之慕。下不失堂构之志。则斯足以有辞于后矣。且夫曹君记述。出于赤心相与。而深得朋友切磋之义。则循是以往。何患乎役于物遗其实哉。惟君其勉之哉。云岩书堂重建记
直桧城之南十里。所有曰云岩书院者。盖愚谷朴公故里。而一方士林因为畏垒之奉者也。当初刱建。在于国家 明陵之世。而祝号谨严。仪物秩备。四时和气之荐。二仲苾芬之升。僾然而如见。肃然而如临。上而寓羹墙之慕。下而效尘刹之报者。讫数百岁而无替矣。斯文不幸。元二告厄。戊辰令甲。遍及于方域。使半亩明宫。亦不免焉。悠悠苍天。此何为哉。画栋雕梁。芜没于榛莽。颓垣破壁。狼籍于沟壑。洋洋陟降之灵。无所于归。则天意人事有足以悽怆而寒心者矣。安得三遇而如常乎。往时一番前辈。忾然发虑。即其旧址而构得数架。以仿颜亭之不忍废。而扁之曰云岩书堂。又设一稧。为游息经用之资。而名之曰尚义。盖将以有为也。五世孙琪焕甫续成前人之志。规恢后日之策。竭其诚故事从而叙。致其力故物随而赡。以之缮理而规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1L 页
 模翼翼。以之增式而科条井井。为之碣以表其神板之所安。为之龛以重其梓绣之所藏。斧堂之密迩也而浇奠以时。时节之追慕也而祼荐如礼。虽未得挽回畴昔之光景。亦庶几乎瞻依之有所。不亦伟哉。虽然君子继述之道。有大于是者。今且服膺乎敬义之牌而思所以直内而方外。留心于心近之书而思所以律身而刑家。日征月迈。勉勉相与。以无负公之遗意。则斯可谓不忘其本而乐其所生者欤。夫如是则之此一堂。不亶为密城氏再振之基。而抑亦有补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方矣。诸君其勉之哉。
模翼翼。以之增式而科条井井。为之碣以表其神板之所安。为之龛以重其梓绣之所藏。斧堂之密迩也而浇奠以时。时节之追慕也而祼荐如礼。虽未得挽回畴昔之光景。亦庶几乎瞻依之有所。不亦伟哉。虽然君子继述之道。有大于是者。今且服膺乎敬义之牌而思所以直内而方外。留心于心近之书而思所以律身而刑家。日征月迈。勉勉相与。以无负公之遗意。则斯可谓不忘其本而乐其所生者欤。夫如是则之此一堂。不亶为密城氏再振之基。而抑亦有补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方矣。诸君其勉之哉。孝子 赠中学教官慕庐庵卢公兄弟旌闾阁记
上之四十二年乙巳。道臣以昌原孝子卢公兄弟孝行卓异事闻于朝。特 赠二公爵中学教官。又命旌其闾以风励四方。盖盛典也。按二公讳正中字福汝其伯也。讳晟中字器汝其季也。兄弟二人。先后生焉。而生则便知爱亲之道。其匍匐而就食也。必先父母之口。其稍长而就傅也。不废晨昏之节。滫瀡必亲检而不懈。应唯必婉顺而无违。其知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2H 页
 能之夙著已如此。而及其遭母夫人丧。弱龄拚号。几至灭性。终三年不近草木之滋。又书揭蓼莪诗于壁上。日三复流涕。非至性而能如是乎。其事先公也。益复洞属。跬步不敢忘。先公偶患风痹。凡起居运动饮食便旋。不须人则不能。公兄弟夙宵侍侧。十年如一日。食上则曰此某馔也。此某羹也。有外闻则曰某处有此事也。某人有此举也。或作婴儿戏如老莱之弄雏。未尝叱犬马如公明之所学。中裙污秽。亲自浣濯如石君家之中郎。皆人所难也。至遭故则公年已不毁。而哀哀孺子哭。有不忍闻者。殓葬诸节。一遵文公家礼。以致自尽之道。衰绖不袪身。逐日省墓。虽风雨不废。樵牧为之治道。有雨雪则争先扫除。称之以孝子程云。驶雨如倾。大川横溢。而苴杖所临。使江水而安流。瑞谷挺出九穗颖栗。而血泪所滋。荓雀鼠而远遁。则此乃天也非人也。昌黎子所谓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时期者非欤。于是乡里耸叹。公议协同。至有褒闻之状。公即取而火之曰使我增益不孝之罪也。因屏迹穷庐。扁其室曰慕庐。各赋四韵以寓终身之慕。朱夫子尝曰求知于世而为之。则虽割股庐墓
能之夙著已如此。而及其遭母夫人丧。弱龄拚号。几至灭性。终三年不近草木之滋。又书揭蓼莪诗于壁上。日三复流涕。非至性而能如是乎。其事先公也。益复洞属。跬步不敢忘。先公偶患风痹。凡起居运动饮食便旋。不须人则不能。公兄弟夙宵侍侧。十年如一日。食上则曰此某馔也。此某羹也。有外闻则曰某处有此事也。某人有此举也。或作婴儿戏如老莱之弄雏。未尝叱犬马如公明之所学。中裙污秽。亲自浣濯如石君家之中郎。皆人所难也。至遭故则公年已不毁。而哀哀孺子哭。有不忍闻者。殓葬诸节。一遵文公家礼。以致自尽之道。衰绖不袪身。逐日省墓。虽风雨不废。樵牧为之治道。有雨雪则争先扫除。称之以孝子程云。驶雨如倾。大川横溢。而苴杖所临。使江水而安流。瑞谷挺出九穗颖栗。而血泪所滋。荓雀鼠而远遁。则此乃天也非人也。昌黎子所谓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无时期者非欤。于是乡里耸叹。公议协同。至有褒闻之状。公即取而火之曰使我增益不孝之罪也。因屏迹穷庐。扁其室曰慕庐。各赋四韵以寓终身之慕。朱夫子尝曰求知于世而为之。则虽割股庐墓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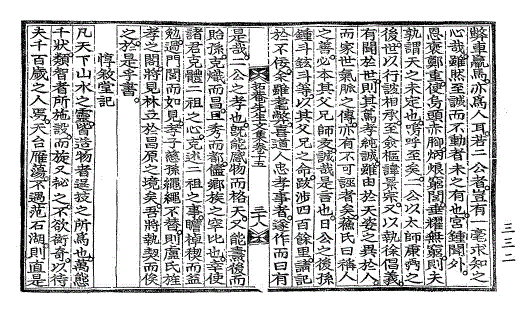 弊车羸马。亦为人耳。若二公者。岂有一毫求知之心哉。虽然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宫钟闻外。 恩褒郑重。使乌头赤脚。炳烺穷闾。垂耀无穷。则夫孰谓天之未定也。呜呼至矣。二公以太师康弼之后。世以行谊相承。至佥枢讳景宗。又以执徐倡义。有闻于世。则其笃孝纯诚。虽由于天姿之异于人。而家世气脉之传。亦有不可诬者矣。苏氏曰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师友。诚哉是言也。日公之后孙钟斗铉斗等。以其父兄之命。跋涉四百馀里。请记于不佞。余虽耄弊。喜道人忠孝事者。遂作而曰有是哉。二公之孝也。既能感物而格天。又能焘后而贻孙。克炽而昌。且秀而都。尽乡族之罕比也。幸使诸君克体二祖之心。克述二祖之事。瞻棹稧而益勉。过门闾而如见。孝子慈孙绳绳不替。则卢氏旌孝之阁。将见林立于昌原之境矣。君将执契而俟之。于是乎书。
弊车羸马。亦为人耳。若二公者。岂有一毫求知之心哉。虽然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宫钟闻外。 恩褒郑重。使乌头赤脚。炳烺穷闾。垂耀无穷。则夫孰谓天之未定也。呜呼至矣。二公以太师康弼之后。世以行谊相承。至佥枢讳景宗。又以执徐倡义。有闻于世。则其笃孝纯诚。虽由于天姿之异于人。而家世气脉之传。亦有不可诬者矣。苏氏曰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师友。诚哉是言也。日公之后孙钟斗铉斗等。以其父兄之命。跋涉四百馀里。请记于不佞。余虽耄弊。喜道人忠孝事者。遂作而曰有是哉。二公之孝也。既能感物而格天。又能焘后而贻孙。克炽而昌。且秀而都。尽乡族之罕比也。幸使诸君克体二祖之心。克述二祖之事。瞻棹稧而益勉。过门闾而如见。孝子慈孙绳绳不替。则卢氏旌孝之阁。将见林立于昌原之境矣。君将执契而俟之。于是乎书。惇叙堂记
凡天下山水之灵。皆造物者逞技之所为也。万态千状。类智者所施设。而旋又秘之。不欲衒奇。以待夫千百岁之人焉。天台雁荡。不遇范石湖。则直是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3H 页
 秽墟而已。桂州龙壁。不经柳柳州。则亦终归于芜没而已。于是余疑造物之有无久矣。今于碧珍氏惇叙之堂。知其诚有。盖宜春素称山水之处。而昭明其望也。洛江其渎也。江自北而来。横亘数十里。浩淼泱漭。如河矶之匹练。明沙夹之。晶晶䁗䁗。照耀人目。如入琼瑶之窟。上浦之水。又西南转而注之江。其岸则翠壁如削。其渚则芦花如雪。而中藏奥区。窅然成别一洞天。非乐清旷而谢嚣尘者。不宜有此。至是碧珍氏得以筑之。东西凡六架。为堂为室为小楼为门廊。以备周旋讲习之用。而山川之美。尽为我有。呜呼异哉。碧珍之族。皆以山花先生为胄。而诗礼相承。蔚然为南州之望。今乃地与人得。灵怪毕露。凭轩眺望。可以豁吾之胸襟。宴坐幽闲。可以颐吾之性灵。读书讲礼于斯而述先王之遗教。酣觞赋诗于斯而叙天伦之乐事。化榛莽为颜色。变鸟吟为弦歌。盖秩秩尔洋洋尔。使山灵水怪恍惚鼓舞于声响之中。而若自以为遭遇之幸。岂所谓美不自美。而因人以彰者非欤。不书所作。是贻山水之怨也。故志之使归刻之。主其事者李君斗锡甫云。
秽墟而已。桂州龙壁。不经柳柳州。则亦终归于芜没而已。于是余疑造物之有无久矣。今于碧珍氏惇叙之堂。知其诚有。盖宜春素称山水之处。而昭明其望也。洛江其渎也。江自北而来。横亘数十里。浩淼泱漭。如河矶之匹练。明沙夹之。晶晶䁗䁗。照耀人目。如入琼瑶之窟。上浦之水。又西南转而注之江。其岸则翠壁如削。其渚则芦花如雪。而中藏奥区。窅然成别一洞天。非乐清旷而谢嚣尘者。不宜有此。至是碧珍氏得以筑之。东西凡六架。为堂为室为小楼为门廊。以备周旋讲习之用。而山川之美。尽为我有。呜呼异哉。碧珍之族。皆以山花先生为胄。而诗礼相承。蔚然为南州之望。今乃地与人得。灵怪毕露。凭轩眺望。可以豁吾之胸襟。宴坐幽闲。可以颐吾之性灵。读书讲礼于斯而述先王之遗教。酣觞赋诗于斯而叙天伦之乐事。化榛莽为颜色。变鸟吟为弦歌。盖秩秩尔洋洋尔。使山灵水怪恍惚鼓舞于声响之中。而若自以为遭遇之幸。岂所谓美不自美。而因人以彰者非欤。不书所作。是贻山水之怨也。故志之使归刻之。主其事者李君斗锡甫云。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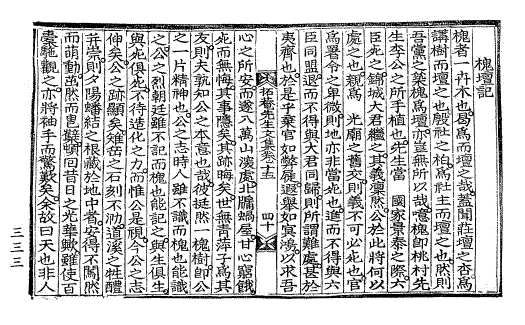 槐坛记
槐坛记槐者一卉木也。曷为而坛之哉。盖闻庄坛之杏。为讲树而坛之也。殷社之柏。为社主而坛之也。然则吾党之筑槐为坛。亦岂无所以哉。噫槐即桃村先生李公之所手植也。先生当 国家景泰之际。六臣死之。锦城大君继之。其义凛然。公于此将何以处之也。亲为 光庙之旧交。则义不可必死也。官为署令之卑微。则地亦非当死也。进而不得与六臣同盟。退而不得与大君同归。则所谓难处。甚于夷齐也。于是乎弃官如弊屣。遐举如冥鸿。以求吾心之所安。而遂入万山深处。北牖蜗屋。甘心穷饿。死而无悔。其事隐矣。其迹晦矣。世无青萍子为其友。则夫孰知公之本意也哉。彼挺然一槐树。即公之一片精神也。公之志时人虽不识而槐也能识之。公之烈朝廷虽不记而槐也能记之。与生俱生。与死俱死。不待造化之力。而惟公是视。今公之志伸矣。公之迹显矣。雉岳之石刻不泐。道溪之牲醴并崇。则夕阳蟠结之根藏于地中者。安得不闯然而萌动。茁然而㽕蘖。顿回昔日之光华欤。虽使百橐驼观之。亦将袖手而惊叹矣。余故曰天也非人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4H 页
 也。坛之西有锦城坛。其前有鸭脚树。即大君游憩之墟。而既毙数百年。郁然复荣。以彰大君之英灵。槐于鸭脚亦类也。谁谓草木之无知哉。兴州之士。既植而坛之。一时之贤士大夫。并为诗歌而张大之。盖天理人情。与槐俱萌者也。公之裔孙宽焘君请余识其事。遂书其所感如此以归之。
也。坛之西有锦城坛。其前有鸭脚树。即大君游憩之墟。而既毙数百年。郁然复荣。以彰大君之英灵。槐于鸭脚亦类也。谁谓草木之无知哉。兴州之士。既植而坛之。一时之贤士大夫。并为诗歌而张大之。盖天理人情。与槐俱萌者也。公之裔孙宽焘君请余识其事。遂书其所感如此以归之。葛野书堂重修记
先王之制。党有庠家有塾。今之书堂。即庠塾之遗制也。其规模之备。教迪之述。虽不逮于古昔。而鲁礼存于饩羊。禹声传于追蠡。则东士大夫之往往营建书堂。岂偶然哉。吾州葛萝山之燕。有所谓高林村者。即我贲趾南先生尸祝之傍。而星霜绵邈。龙汉浩淼。行过洞门。往往有白鹿榛莽之感。近有士人权有圭,有昌兄弟。侨居于是。以攻艺为事。为一方先。而其胤子纬镐,永镐。同里金炳玟,禹洪八相与铅椠之暇。慨然慕庠塾之风。蓄力而拮据之。鸠材而经始之。乃于壬申某月日。创建五架三间于所居之侧。东西二室。所以备秋冬也。中为一堂。所以待春夏也。昔日之樵原牧场。变作艺游之所。昔日之山讴野咏。化为歌诵之音。噫不有以溉其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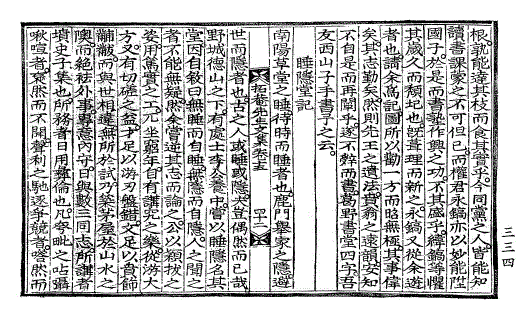 根。孰能达其枝而食其实乎。今同党之人。皆能知读书课蒙之不可但已。而权君永镐亦以妙能升国子。于是而书塾作兴之功。不其盛乎。纬镐等惧其岁久而颓圮也。既葺理而新之。永镐又从余游者也。请余为记。图所以劝一方而昭无极。其事伟矣。其志勤矣。然则先王之遗法。贲翁之远韵。安知不自是而再阐乎。遂不辞而书。葛野书堂四字。吾友西山子手书予之云。
根。孰能达其枝而食其实乎。今同党之人。皆能知读书课蒙之不可但已。而权君永镐亦以妙能升国子。于是而书塾作兴之功。不其盛乎。纬镐等惧其岁久而颓圮也。既葺理而新之。永镐又从余游者也。请余为记。图所以劝一方而昭无极。其事伟矣。其志勤矣。然则先王之遗法。贲翁之远韵。安知不自是而再阐乎。遂不辞而书。葛野书堂四字。吾友西山子手书予之云。睡隐堂记
南阳草堂之睡。待时而睡者也。鹿门举家之隐。避世而隐者也。古之人或睡或隐。夫岂偶然而已哉。野城德山之下。有处士李公养中。尝以睡隐名其堂。因自叙曰无睡而自睡。无隐而自隐。人之闻之者不能无疑。然余尝逆其志而论之。公以颖拔之姿。用笃实之工。兀坐穷年。自有讲究之乐。从游大方。又有切磋之益。才足以游刃盘错。文足以贲饰黼黻。而与世相违。无所于试。乃筑茅屋于山水之隩。而绝袪外事。专意内守。日与数三同志。所讲者坟史子集也。所务者日用彝伦也。凡夸毗之呫嗫啾喧者。褒然而不闻。声利之驰逐争竞者。㗳然而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5H 页
 不顾。不必阖眼牢睡而不可谓非睡也。不必晦迹遐举而不可谓非隐也。游神于黑甜之乡而不睡者存焉。托迹于寒流之涧而非隐者在焉。如是而谓之不睡可乎。谓之无隐可乎。公之所以为睡隐者。良以是欤。呜呼。公之家势不振。堂废而墟者久矣。其曾孙光乙衋然追慕。图所以葺理旧架。而请记于余。余窃悲其志。遂略缀而为记。
不顾。不必阖眼牢睡而不可谓非睡也。不必晦迹遐举而不可谓非隐也。游神于黑甜之乡而不睡者存焉。托迹于寒流之涧而非隐者在焉。如是而谓之不睡可乎。谓之无隐可乎。公之所以为睡隐者。良以是欤。呜呼。公之家势不振。堂废而墟者久矣。其曾孙光乙衋然追慕。图所以葺理旧架。而请记于余。余窃悲其志。遂略缀而为记。九峰亭重建记
直月城北数舍许杞溪之里。有曰九峰亭者。即李氏诸公为其先祖施设者也。谓之九峰者何也。盖李之先祖教官公尝以笃孝至行。侍庐于九川之山。一荐三载。血泪彻壤。而明发不寐之恸。愈久不衰。故撤庐而归。犹以九峰自称。以志其不忘。君子所谓终身慕者非欤。公既没。后嗣子孙之居于是邦者。怵然惕然。各自以祖先之心为心。即其先公起居之墟。而规置数间屋子。为永世墙羹之所。而日月寝绵。风雨动摇。居然为菟葵燕麦之场久矣。李氏诸公为是之衋然。协力发虑。图所以肯构。乃于庚子春。买得七架屋于旧墟。而更以两翼增之。以涂以茨以斲以砻。阅五六朔而功告讫。左右为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5L 页
 室凡四架。前后为堂亦五架。统之为九架。而以九峰二字揭之于楣。盖轮焉尔焕焉尔。庶几在天之灵。陟降于斯。悦豫于斯。而安知不曰余有后乎。于乎。先公孺慕之孝。以是号而益著。后孙追远之孝。以是阁而愈远。则孝之一字。即李氏家箕裘之物耳。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又曰君子有孝子。永锡祚胤。窃为诸公诵之。
室凡四架。前后为堂亦五架。统之为九架。而以九峰二字揭之于楣。盖轮焉尔焕焉尔。庶几在天之灵。陟降于斯。悦豫于斯。而安知不曰余有后乎。于乎。先公孺慕之孝。以是号而益著。后孙追远之孝。以是阁而愈远。则孝之一字。即李氏家箕裘之物耳。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又曰君子有孝子。永锡祚胤。窃为诸公诵之。舒养斋记
人之有生也。气以成形而精神寓焉。理具于心而性情该焉。以其寓于形。故不有以发舒。则易有昏惰之患。以其具于心。故不有以涵养。则易有斲丧之失。可不惧哉。南塘陈氏夙夜之箴。特以发舒精神。体养情性。为动静交养之要者。盖以此也。吾党有卞君宰铉甫。尝缚茅于先亭之侧。以为卒岁栖息之所。而扁之曰舒养。实取南塘之箴意也。因以请记于余。余非能言者。然盖尝闻之。君子之学。通贯动静。故其动也必以发舒为贵。朱子所谓玩物适情。退陶所谓看山玩水是也。其静也必以存养为主。大易所谓向晦燕息。程子所谓涵养本原是也。今使吾子处于斯游于斯从事于斯。动焉而舒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6H 页
 其神。以验夫静之所存。静焉而养其性。以涵夫动之所本。则日用之间。无非舒养。而周夫子太极图动静贯一之妙。可得以言矣。此吾与子之所当竭力而求至焉者。盍相与勉之哉。于是作舒养斋记。
其神。以验夫静之所存。静焉而养其性。以涵夫动之所本。则日用之间。无非舒养。而周夫子太极图动静贯一之妙。可得以言矣。此吾与子之所当竭力而求至焉者。盍相与勉之哉。于是作舒养斋记。孝子默窝郑公旌闾阁记
上之二十五年戊子。廷臣有以彦阳士人郑在勋孝行荐闻者。 上特命该曹 赠爵童蒙教官。又令道臣亟施棹楔之典。乌头赤脚。辉映闾里。于是而郑公之孝。大显于世。于乎伟矣。公非有师友见闻之益。而知能夙著于妙龄。行解不畔于彝常。其事生也耕稼以供滫瀡。渔樵以养志体。又得贤配李氏。一心洞属。忠养备至。盖其天性然也。尝于京师之行。忽心惊促还。则父病已弥留矣。公躬执汤饵。稽颡北辰。至有尝粪之诚。人以庾孱陵比之。其送终也。既殡而哀号仆地。几至灭性。既祥而痛霣靡逮。莪泪沾衿。每日哀省于坟所。风雨不废。忽值山溪㬥溢不得渡。方号泣上下之际。溪水中断成路。若有相之者。盖至诚所感也。君子所谓孝弟通于神明者非欤。噫公之馀力学问。亦自一诚字做去。故少而服膺乎小学之篇。长而潜心于洛建之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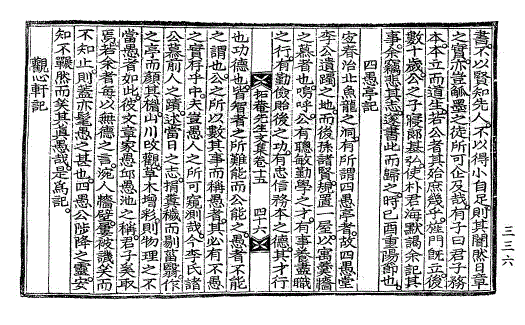 书。不以贤知先人。不以得小自足。则其闇然日章之实。亦岂觚墨之徒所可企及哉。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若公者其殆庶几乎。旌门既立。后数十岁。公之子寝郎基弘。使朴君海默谒余记其事。余窃悲其志。遂书此而归之。时己酉重阳节也。
书。不以贤知先人。不以得小自足。则其闇然日章之实。亦岂觚墨之徒所可企及哉。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若公者其殆庶几乎。旌门既立。后数十岁。公之子寝郎基弘。使朴君海默谒余记其事。余窃悲其志。遂书此而归之。时己酉重阳节也。四愚亭记
宜春治北鱼龙之洞。有所谓四愚亭者。故四愚堂李公遗躅之地。而后孙诸贤。规置一屋。以寓羹墙之慕者也。呜呼。公有聪敏勤学之才。有事养尽职之行。有勤俭贻后之功。有忠信务本之德。其才行也功德也。皆智者之所难能而公能之。愚者不能之谓也。公之所以数其事而称愚者。其必有不愚之实存乎中。夫岂愚人之所可窥测哉。今李氏诸公慕前人之迹。述当日之志。捐粪秽而剔菑翳。作之亭而颜其楣。山川改观。草木增彩。则物理之不当愚者如此。彼文章家愚邱愚池之称。君子奚取焉。若余者每以无德之言。涴人墙壁。屡被讥笑而不知止。则盖亦髦愚之甚也。四愚公陟降之灵。安知不冁然而笑其真愚哉。是为记。
观心轩记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7H 页
 心之为物。如明镜止水。应物无迹。而有邪正之分者。以其物欲之交蔽故耳。苟为物欲所牵去。荡焉而不知返。则其流必至于祸家倾身而后已。岂不哀哉。金君德俊。海上之隐士也。其孙泳学从予于寂寞之滨。知教导之甚严也。意甚嘉之。名其轩曰观心。盖取禅家面璧观心之语也。君以三吾之子。养蒙之侄。亲承庭训。纤啬作业。家刀稍饶。而收拾二公遗唾。传布于世。又别立祠宇。与一方衿绅共举褥仪。以享百世。非但为先之诚有足以感动人者。方且嗜利之心。急于洪水猛兽。而捐金独担。不知有其射。岂不美哉。愿君朝夕观省。以为治心之单方。则与卫武公九十箴儆者。奚以异焉。勉之哉。
心之为物。如明镜止水。应物无迹。而有邪正之分者。以其物欲之交蔽故耳。苟为物欲所牵去。荡焉而不知返。则其流必至于祸家倾身而后已。岂不哀哉。金君德俊。海上之隐士也。其孙泳学从予于寂寞之滨。知教导之甚严也。意甚嘉之。名其轩曰观心。盖取禅家面璧观心之语也。君以三吾之子。养蒙之侄。亲承庭训。纤啬作业。家刀稍饶。而收拾二公遗唾。传布于世。又别立祠宇。与一方衿绅共举褥仪。以享百世。非但为先之诚有足以感动人者。方且嗜利之心。急于洪水猛兽。而捐金独担。不知有其射。岂不美哉。愿君朝夕观省。以为治心之单方。则与卫武公九十箴儆者。奚以异焉。勉之哉。七友亭记
宜春有隐君子。即寝郎周七甫也。公有七子。当甲日设寿宴祝冈陵。公遂命之曰吾少也。贫不得从师就学。所望在于汝曹。而既无义方之教。居然之顷。年有六十一矣。拊念畴昔。慨叹何及哉。乃出若干金为契。名曰七友。逐年拮据。营立一堂。备子孙肄业之所。又仿古义田宅例。周宗族之贫乏者。乡里有穷不能资学者。并许就学。此平生所愿。汝曹
拓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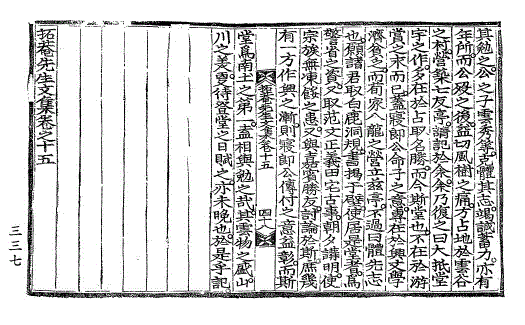 其勉之。公之子云秀等。克体其志。竭诚蓄力。亦有年所。而公殁之后。益切风树之痛。方占地于云谷之村。营筑七友亭。请记于余。余乃复之曰大抵堂宇之作。多在于占取名胜。而今斯堂也。不在于游赏之求而已。盖寝郎公命子之意。专在于兴文学济贫乏。而荀家八龙之营立玆亭。不过曰体先志也。愿诸君取白鹿洞规。书揭于壁。使居是堂者。为警省之资。又取范文正义田宅古事。朝夕讲明。使宗族无冻馁之患。又与嘉宾胜友。讨论于斯。庶几有一方作兴之渐。则寝郎公传付之意益彰。而斯堂为南土之第一。盍相与勉之哉。其云物之盛。山川之美。更待登堂之日赋之。亦未晚也。于是乎记。
其勉之。公之子云秀等。克体其志。竭诚蓄力。亦有年所。而公殁之后。益切风树之痛。方占地于云谷之村。营筑七友亭。请记于余。余乃复之曰大抵堂宇之作。多在于占取名胜。而今斯堂也。不在于游赏之求而已。盖寝郎公命子之意。专在于兴文学济贫乏。而荀家八龙之营立玆亭。不过曰体先志也。愿诸君取白鹿洞规。书揭于壁。使居是堂者。为警省之资。又取范文正义田宅古事。朝夕讲明。使宗族无冻馁之患。又与嘉宾胜友。讨论于斯。庶几有一方作兴之渐。则寝郎公传付之意益彰。而斯堂为南土之第一。盍相与勉之哉。其云物之盛。山川之美。更待登堂之日赋之。亦未晚也。于是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