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经义
经义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0H 页
 小学
小学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云云。
夫道也者。秉彝之心。虽有秉彝之心。而饱其食暖其衣。则嬉嬉放逸。而不孝于父。不忠于君。不别于夫妇。不序于长幼。不信于朋友。此亦便是禽兽也。故惟圣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使之父慈子孝而有亲焉。君仁臣忠而有义焉。夫妇如宾而有别焉。长先幼后而有序焉。朋友切偲而有信焉。亦因其固有而导之也。
命夔曰命汝典乐。止神人以和。
夔长于音乐者也。故命之而典乐者。所以变化气质者也。故使之教胄子。如下文所云也。凡人直者不足于温。故欲其温。宽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刚者必至于虐。故欲其无虐。简者必至于傲。故欲其无傲。而非乐则不能如是变化也。然乐又不可不知也。诗言其所以乐之志。歌永其所言。声依其所永。律和其所依之声。而各有条理。不或错乱。故被之八音则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亦各得其所。故翕然和谐。无失伦次。而祭以奏之则神明降格。礼以作之则民人感化。而中和之德。至矣尽矣。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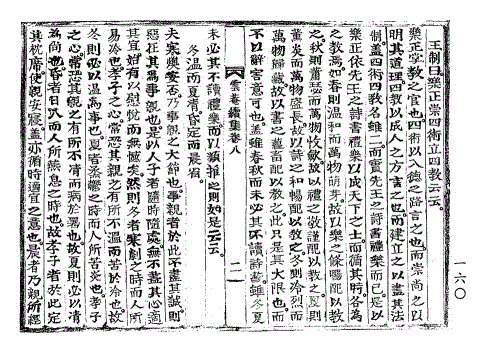 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云云。
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云云。乐正掌教之官也。四术以入德之路言之也。而崇尚之以明其道理。四教以成人之方言之也。而建立之以尽其法制。盖四术四教名虽二。而实先王之诗书礼乐而已。是以乐正依先王之诗书礼乐以成天下之士。而循其时。各为之教焉。如春则温和而万物萌芽。故以乐之条畅配以教之。秋则萧瑟而万物收敛。故以礼之敬谨配以教之。夏则薰炎而万物盛长。故以诗之和畅配以教之。冬则冷烈而万物归藏。故以书之蕴畜配以教之。此只是其大限也。而不以辞害意可也。盖虽春秋而未必其不读诗书。虽冬夏未必其不读礼乐。而以类推之则如是云云。
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夫寒燠安否。乃事亲之大节也。事亲者于此不尽其诚。则恶在其为事亲也。是以人子者随时随处。无不尽其心适其宜。始有以慰悦而无憾矣。然则冬者寒剧之时而人所易冷也。孝子之心。常恐其亲之有所不温而苦于冷也。故冬则必以温为事也。夏者烝郁之时而人所苦炎也。孝子之心。常恐其亲之有所不凊而病于暑也。故夏则必以凊为尚也。昏者日入而人所燕息之时也。故孝子者于此定其枕席。使亲安寝。盖亦循时适宜之意也。晨者乃亲所经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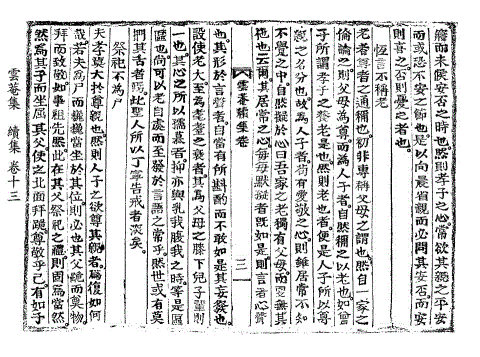 寝而未候安否之时也。然则孝子之心。常欲其亲之平安而或恐不安之节也。是以向晨省亲而必问其安否。而安则喜之。否则忧之者也。
寝而未候安否之时也。然则孝子之心。常欲其亲之平安而或恐不安之节也。是以向晨省亲而必问其安否。而安则喜之。否则忧之者也。恒言不称老
老者尊者之通称也。初非专称父母之谓也。然自一家之伦论之。则父母为尊。而为人子者。自然称之以老也。如曾子所谓孝子之养老是也。然则老也者。便是人子所以尊亲之名分也。故为人子者。苟有爱敬之心。则虽居常不知不觉之中。自然拟于心曰吾家之老独有父母。而更无其他也云尔。其居常之心。每每默拟者既如是。则言者心声也。其形于言声者。自当有所斟酌而不敢如是其妄发也。设使老大。至为耄耋之衰者。其为父母之膝下儿子辈则一也。其心之所以孺慕者。抑亦与乳我腹我之时。等是区区也。尚可以老自处而至发于言语之常乎。然世或有莫扪其舌者焉。此圣人所以丁宁告戒者深矣。
祭祀不为尸
夫孝莫大于尊亲也。然则人子之欲尊其亲者。为复如何哉。若夫为尸而巍巍当坐于其位。则必也其父跪而奠物。拜而致敬。如事祖先然。此在其父祭祀之礼。则固为当然。然为其子而坐屈其父。使之北面拜跪。尊敬乎己。有如子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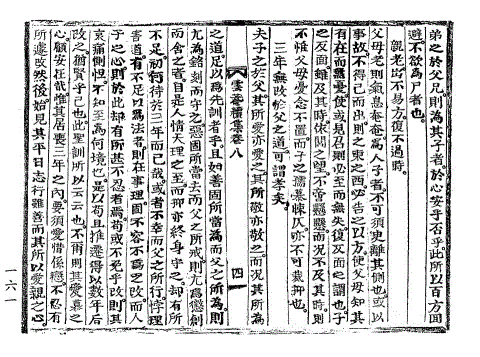 弟之于父兄。则为其子者。于心安乎否乎。此所以百方回避。不欲为尸者也。
弟之于父兄。则为其子者。于心安乎否乎。此所以百方回避。不欲为尸者也。亲老。出不易方。复不过时。
父母老则气息奄奄。为人子者。不可须臾离其恻也。或以事故。不得已而出。则之东之西。必告之以方。使父母知其有在而无忧。使或见召则必至而无失。复反面之谓也。子之反面。虽及其时。依闾之望。不啻悬悬。而况不及其时。则不惟父母忧念不置。而子之孺慕悚仄。亦不可裁抑也。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夫子之于父。其所爱亦爱之。其所敬亦敬之。而况其所为之道。足以为先训者乎。且如善固所当为而父之所为。则尤为铭刻而守之。恶固所当去而父之所戒。则尤为惩创而舍之者。自是人情天理之至。而抑亦终身守之。却有所不足。初何待于三年而已哉。或者不幸而父之所行。悖理害道。有不足以为法者。则在事理。固不容不为之改。而人子之心。则于此却有所甚不忍者焉。苟或不免乎改。则其哀痛恻怛。不知至为何境也。是以苟且推迁得以数年后改之。犹贤乎已也。此圣训所以云云也。不尔则其爱慕之心。顾安在哉。惟其居丧三年之内。要须爱惜系恋。不忍有所遽改然后。始见其平日志行虽善而其所以爱亲之心。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2H 页
 则固未尝不为之恻怛。恻怛区区。有并行不悖者矣。
则固未尝不为之恻怛。恻怛区区。有并行不悖者矣。曲礼曰。君子虽贫。不粥祭器云云。
曲礼曰。为人子之爱亲也。事死如事生。故虽贫不能食。而不忍粥祭器。虽寒无所著。而不忍服祭衣。虽欲作宫室。而不忍斩丘木。以考妣之祭享。重于己之身口也。若不爱亲者。只知己之腹饥。而不知考妣之饥重于己。只知己之身寒。而不知考妣之寒重于己也。只知己作宫室。而不知考妣之依托重于己也。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云云。
夫人之于亲。情理则不无亲疏。而其地位则却与吾亲同是人也。既与吾亲同是人也。则爱亲者其得只爱其亲。而不为推爱于与亲同是之人乎。敬亲者其得只敬其亲。而不为推敬于与亲同是之人乎。是故人之真个致爱于亲。无不用极。则必不只爱其亲也。其心自当于人恻然思有以推其恩爱之均也。真个致敬于亲。如恐不及。则必不只敬其亲也。其心自当于人肃然思有以推其恭敬之均也。若夫只爱其亲而恶于人。则其所以爱亲者。恐亦有所未尽也。只敬其亲而慢于人。则其所以敬亲者。亦有所未尽也。盖源深而流不放海者。未之有也。本固而挺不参天者。亦未之有也。
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2L 页
 人之口腹。虽得甘味之养。而心志闷菀。不得以自安。则其得为养老之孝乎。故为子者。不骄不乱不争。使父母之心得以自安。则虽菽水之养。不至为不孝矣。若骄而至于亡。乱而至于刑。争而至于兵。则为其亲者。自不免危戮矣。虽日以牛羊豕之盛。供其父母。岂得为孝乎。
人之口腹。虽得甘味之养。而心志闷菀。不得以自安。则其得为养老之孝乎。故为子者。不骄不乱不争。使父母之心得以自安。则虽菽水之养。不至为不孝矣。若骄而至于亡。乱而至于刑。争而至于兵。则为其亲者。自不免危戮矣。虽日以牛羊豕之盛。供其父母。岂得为孝乎。君言。不宿于家。
君言即天命也。为使者其敢不敬乎。故既受君言。则不敢迟滞。朝而受命。则夕而出行矣。不敢归宿于家。待明日而行也。故孔子于君召。不俟驾而行。即此言也。
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
盖果之有核者。固当弃之也。然在他人之前。则弃之可也。至于君前。则其尊无上。其严非常。万一食果于其前。则虽核之可弃者。岂敢弃之。有如他人之前而累其君侧乎。故赐果于君前。则为其臣下者。俯伏畏缩而食之。其核则不可食。亦不可弃之以累君侧。故不得已置其核于怀中而出。盖敬之至义之尽也。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君命之至。为臣者虽暂时之间。岂敢坐以待其所欲乎。故其趍君命也。固知我步则迟。彼车则疾。而虽先行。决不及车矣。然君命之召。而欲以坐待其驾。则于心有所不矣。故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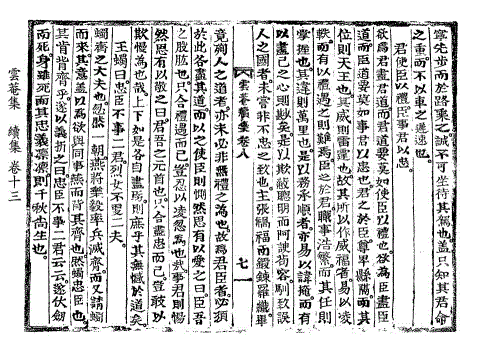 宁先步而于路乘之。诚不可坐待其驾也。盖只知其君命之重。而不以车之迟速也。
宁先步而于路乘之。诚不可坐待其驾也。盖只知其君命之重。而不以车之迟速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欲为君尽君道。而君道要莫如使臣以礼也。欲为臣尽臣道。而臣道要莫如事君以忠也。君之于臣。尊卑县隔。而其位则天王也。其威则雷霆也。故其所以作威福者。易以凌轶。而有以礼遇之则难焉。臣之于君。职事浩繁。而其任则掌握也。其违则万里也。是以务承顺者。亦易以讳掩。而有以尽己之心则鲜矣。是以欺蔽聪明而阿谀苟容。驯致误人之国者。未尝非不忠之致也。主张祸福而锻鍊罗织。毕竟殉人之道者。亦未必非无礼之为也。故为君臣者。必须于此各尽其道。而以之使臣则恻然思有以爱之曰。臣吾之股肱也。只合礼遇而已。岂忍以凌忽为也哉。事君则惕然思有以敬之曰。君吾之元首也。只合尽忠而已。岂敢以欺慢为也哉。上下如是各自尽焉。则庶乎其无憾于道矣。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蠋齐之大夫也。忽然一朝。燕将乐毅率兵灭齐。而又请蠋而来。其意盖以为欲与同事燕而背其齐也。然蠋忠臣也。其肯背齐乎。遂以义折之曰。忠臣不事二君云云。遂伏剑而死。身虽死而其忠义凛凛。则千秋尚生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3L 页
 男子亲迎。止其义一也。
男子亲迎。止其义一也。夫婚姻之礼。万世之大本也。而所以男先于女者。以其刚柔之义也。其亲迎之时。不使他人而躬往迎之。刚必先于柔也。盖刚何谓之刚。柔何谓之柔。曰刚指其男子健壮之象。健壮则有力。足以统率。故先乎女。柔指其女子柔顺之象。柔顺则无力。只能依附。故后乎男。然非独男女之义为若是而已。虽天地之义。亦有刚柔之分。故天造始而地代终。阳气温燠。雨露浃洽。然后冰解冻释。万物畅茂。此天先乎地也。君臣之分。亦有刚柔。故君主倡而臣主和。必以命令先之。然后臣忠顺成之。此君先乎臣也。以此观之。天地君臣交合之义。亦与男先乎女。为一般道理而非有二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夫文者六经之谓也。而义理精深。非自家一人聪明所能尽其底蕴者也。必有多闻博学之友。竭其智虑。合其论议。为之研几钻坚。穷深极微。始有以转暗为明。扩小为大。而自家所见所识。极乎高明矣。仁者志笃行实之谓也。然则志虑之真实。行检之高明。只在自家所为如何而难仰他人也。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也。何关于朋友之辅乎。盖决意独往。孜孜不已。则固自己所任。而人不与焉。然其于日用间私意之克而未尽者。天理之复而未及者。自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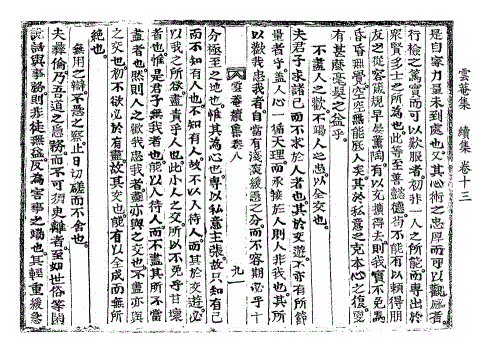 是自家力量未到处也。又其心术之忠厚而可以观感者。行检之笃实而可以叹服者。初非一人之所能。而专出于众贤多士之所为也。此等至善懿德。苟不能有以赖得朋友之从容箴规早晏薰陶。有以充扩得去。则我实不免为昏昏无觉。空空无能底人矣。其于私意之克本心之复。更有甚么毫发之益乎。
是自家力量未到处也。又其心术之忠厚而可以观感者。行检之笃实而可以叹服者。初非一人之所能。而专出于众贤多士之所为也。此等至善懿德。苟不能有以赖得朋友之从容箴规早晏薰陶。有以充扩得去。则我实不免为昏昏无觉。空空无能底人矣。其于私意之克本心之复。更有甚么毫发之益乎。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夫君子求诸己而不求于人者也。其于交游。不亦有所节量者乎。盖人心一循天理。而承接于人则人非我也。其所以欢我忠我者。自当有浅深缓急之分。而不容期必乎十分极至之地也。惟其为心也。专以私意主张。故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不知有人。故不以人待人。而其于交游。必以我之所欲。尽责乎人也。此小人之交。所以不免乎甘坏者也。惟是君子无我者也。能以人待人。而不尽其所不当尽者也。然则人之欢我忠我者。尽亦与之交也。不尽亦与之交也。初不欲必于有尽。故其交也。能有以全成而无所绝也。
无用之辩。不急之察。止日切磋而不舍也。
夫彝伦。乃吾道之急务。而不可须臾离者。至如世俗等闲说话与事务。则非徒无益。反为害事之端也。其轻重缓急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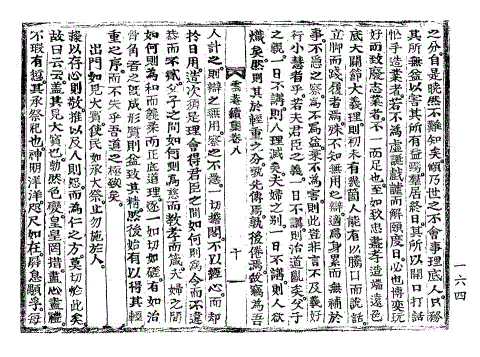 之分。自是晓然不难知矣。顾乃世之不会事理底人。只务其所无益以害其所有益焉。群居终日。其所以开口打话忙手造业者。若不为虚诞戏谑而解颐度日。必也博奕玩好而致废志业者。不一而足也。至如致忠尽孝造端远色底大关节大义理。则初未有几个人能有以腾口而说话。立脚而践履者焉。殊不知无用之辩。适为身累而无补于事。不急之察。为不为益。弃不为害。则此岂非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者乎。若夫君臣之义。一日不讲。则治道乱矣。父子之亲。一日不讲。则人理灭矣。夫妇之别。一日不讲。则人欲炽矣。然则其于轻重之分。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故窃为吾人计之。则辩之无用。察之不急。一切担阁。不以经心。而却于日用。造次须是理会得君臣之间如何则为令而不违恭而不贰。父子之间如何则为慈而教孝而箴。夫妇之间如何则为和而义柔而正底道理。逐一如切如磋。有如治骨角者之既成形质则益致其精。然后始有以得其轻重之序。而不失乎吾道之极致矣。
之分。自是晓然不难知矣。顾乃世之不会事理底人。只务其所无益以害其所有益焉。群居终日。其所以开口打话忙手造业者。若不为虚诞戏谑而解颐度日。必也博奕玩好而致废志业者。不一而足也。至如致忠尽孝造端远色底大关节大义理。则初未有几个人能有以腾口而说话。立脚而践履者焉。殊不知无用之辩。适为身累而无补于事。不急之察。为不为益。弃不为害。则此岂非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者乎。若夫君臣之义。一日不讲。则治道乱矣。父子之亲。一日不讲。则人理灭矣。夫妇之别。一日不讲。则人欲炽矣。然则其于轻重之分。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故窃为吾人计之。则辩之无用。察之不急。一切担阁。不以经心。而却于日用。造次须是理会得君臣之间如何则为令而不违恭而不贰。父子之间如何则为慈而教孝而箴。夫妇之间如何则为和而义柔而正底道理。逐一如切如磋。有如治骨角者之既成形质则益致其精。然后始有以得其轻重之序。而不失乎吾道之极致矣。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止勿施于人。
操以存心则敬。推以及人则恕。而为仁之方。莫切于此矣。故曰云云。盖其见大宾也。勃然色变。皇皇罔措。尽心尽礼。不瑕有愆。其承祭祀也。神明洋洋。咫尺如在。屏息颙孚。每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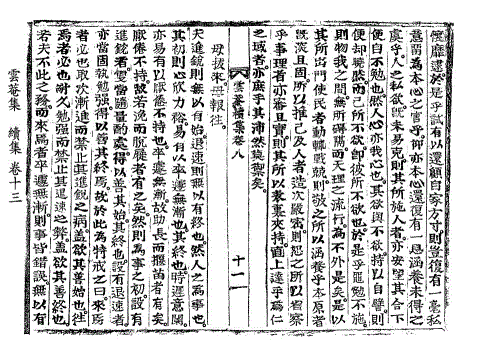 怀靡逮。于是乎试有以还顾自家方寸。则岂复有一毫私意留为本心之害乎。抑亦本心还复有一息涵养未得之虞乎。人之私欲。既未易克。则其所施人者。亦安望其合下便自不勉也。然人心亦我心也。其欲与不欲。持以自譬。则便却晓然。而己所不欲。即彼所不欲也。于是乎黾勉不施。则物我之间。无所碍隔。而天理之流行。为不外是矣。是以其所出门使民者动辄战兢。则敬之所以涵养乎本原者既深且固。所以推己及人者造次严密。则恕之所以省察乎事理者亦审且实。则其所以表里夹持。直上达乎为仁之域者。亦庶乎其沛然莫御矣。
怀靡逮。于是乎试有以还顾自家方寸。则岂复有一毫私意留为本心之害乎。抑亦本心还复有一息涵养未得之虞乎。人之私欲。既未易克。则其所施人者。亦安望其合下便自不勉也。然人心亦我心也。其欲与不欲。持以自譬。则便却晓然。而己所不欲。即彼所不欲也。于是乎黾勉不施。则物我之间。无所碍隔。而天理之流行。为不外是矣。是以其所出门使民者动辄战兢。则敬之所以涵养乎本原者既深且固。所以推己及人者造次严密。则恕之所以省察乎事理者亦审且实。则其所以表里夹持。直上达乎为仁之域者。亦庶乎其沛然莫御矣。毋拔来。毋报往。
夫进锐则无以有始。退速则无以有终也。然人之为事也。其初则心欣力裕。易有以卒遽无渐也。其终也。时迟意阑。亦易有以厌倦不持也。卒遽无渐。故助长而揠苗者有矣。厌倦不持。故若浼而脱屣者有之矣。然则为事之初。设有进锐者。更当随量酌处。得以善其始。其终也。设有退速者。亦当固执勉强。得以善其终焉。故于此为特戒之曰。来焉者必也取次渐进而禁止其进锐之病。盖欲其善始也。往焉者必也耐久勉强而禁止其退速之弊。盖欲其善终也。若夫不此之务。而来焉者卒遽无渐。则事皆错误。无以有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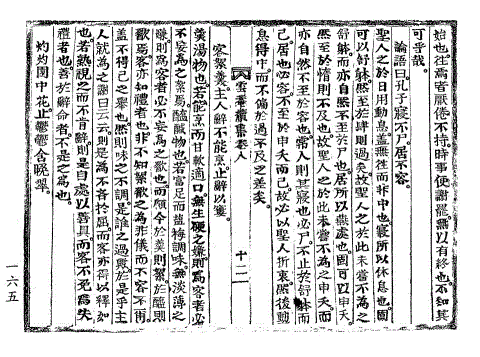 始也。往焉者厌倦不持。时事便谢罢。无以有终也。不知其可乎哉。
始也。往焉者厌倦不持。时事便谢罢。无以有终也。不知其可乎哉。论语曰。孔子寝不尸。居不容。
圣人之于日用动息。盖无往而非中也。寝所以休息也。固可以舒体。然至于肆则过矣。故圣人之于此未尝不为之舒体。而亦自然不至于尸也。居所以燕处也。固可以申夭。然至于惰则不及也。故圣人之于此未尝不为之申夭。而亦自然不至于容也。常人则其寝也必尸。不止于舒体而已。居也必容。不至于申夭而已。故必以圣人折衷。然后动息得中。而不偏于过不及之差矣。
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止辞以窭。
羹汤物也。若能烹而甘软适口。无生硬之嫌。则为客者必不妄为之絮焉。醢咸物也。若富足而盐梅调味。无淡薄之嫌。则为客者必不妄为之歠也。而顾今于羹则絮。于醯则歠焉。客亦知礼者也。非不知絮歠之为非仪而不容不尔。盖不得已之举也。然则味之不调。是谁之过欤。于是乎主人就为之谢曰云云。则是为不吝于屈。而客亦得以释如也。若熟视之而不肯辞。则是自处以善具。而客不免为失礼者也。善于辞命者。不是之为也。
灼灼园中花。止郁郁含晚翠。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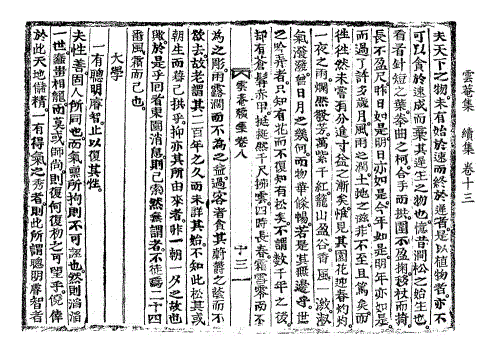 夫天下之物。未有始于速而终于迟者。是以植物者。亦不可以贪于速成而弃其迟生之物也。忆昔涧松之始生也。看看针短之叶。拳曲之柯。合手而拱。围不盈掬。移杖而掎。长不盈尺。昨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而过了许多岁月。风雨之润。土地之滋。非不至且笃矣。而往往然未尝有分进寸益之渐矣。惟见其园花迎春灼灼。一夜之雨。烂然发芳。万紫千红。笼山盈谷。香风一激。淑气泼泼。曾日月之几何。而物华条畅。若是其无边乎。世之吟弄者。只知有花而不复知有松矣。不谓数千年之后。却有苍髯赤甲。挺挺然千尺拂云。四时长春。霜雪零而不为之彫。雨露阔而不为之益。过客者贪其蔚郁之荫而不欲去。故老谓其二百年之久而未详其始。不知此松其或朝生而暮已拱乎。抑亦其所由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欤。于是乎回看东园消息。则已索然无谓者。不徒为二十四番风霜而已也。
夫天下之物。未有始于速而终于迟者。是以植物者。亦不可以贪于速成而弃其迟生之物也。忆昔涧松之始生也。看看针短之叶。拳曲之柯。合手而拱。围不盈掬。移杖而掎。长不盈尺。昨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而过了许多岁月。风雨之润。土地之滋。非不至且笃矣。而往往然未尝有分进寸益之渐矣。惟见其园花迎春灼灼。一夜之雨。烂然发芳。万紫千红。笼山盈谷。香风一激。淑气泼泼。曾日月之几何。而物华条畅。若是其无边乎。世之吟弄者。只知有花而不复知有松矣。不谓数千年之后。却有苍髯赤甲。挺挺然千尺拂云。四时长春。霜雪零而不为之彫。雨露阔而不为之益。过客者贪其蔚郁之荫而不欲去。故老谓其二百年之久而未详其始。不知此松其或朝生而暮已拱乎。抑亦其所由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欤。于是乎回看东园消息。则已索然无谓者。不徒为二十四番风霜而已也。大学
一有聪明睿智。止以复其性。
夫性善。固人所同也。而气禀所拘则不可诬也。然则滔滔一世。蠢蚩相笼。而莫或师尚。则复何复初之可望乎。侥倖于此天地储精。一有得气之秀者。则此所谓聪明睿智者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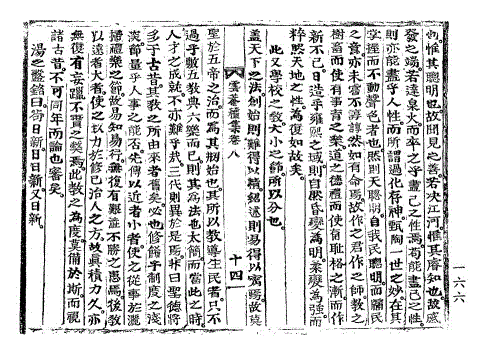 也。惟其聪明也。故闻见之善。若决江河。惟其睿知也。故感发之端。若达泉火。而卒之乎尽己之性焉。苟能尽己之性。则亦能尽乎人性。而所谓过化存神。甄陶一世之妙。在其掌握而不动声色者也。然则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而牖民之意。亦未尝不谆谆然如有命焉。故作之君作之师。教之树畜而使有事育之乐。道之德礼而使有耻格之渐。而作新不已。日造乎雍熙之域。则自然昏变为明。柔变为强。而粹然天地之性。为复如故矣。
也。惟其聪明也。故闻见之善。若决江河。惟其睿知也。故感发之端。若达泉火。而卒之乎尽己之性焉。苟能尽己之性。则亦能尽乎人性。而所谓过化存神。甄陶一世之妙。在其掌握而不动声色者也。然则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而牖民之意。亦未尝不谆谆然如有命焉。故作之君作之师。教之树畜而使有事育之乐。道之德礼而使有耻格之渐。而作新不已。日造乎雍熙之域。则自然昏变为明。柔变为强。而粹然天地之性。为复如故矣。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盖天下之法。创始则难得以精。绍述则易得以密焉。故莫圣于五帝之治。而为其刱始也。其所以教导生民者。只不过乎敷五教典六乐而已。则其为法也太简。而当此之时。人才之成就。不亦难乎哉。三代则异于是焉。非曰圣德将多于古昔。其教之所由来者旧矣。必也修饰乎制度之浅深。节量乎人事之能否。先传以近者小者。使之从事于洒扫礼乐之节。故易知易行。无复有艰涩不胜之患焉。后教以远者大者。使之致力于修己治人之方。故真积力久。亦无复有妄躐不实之弊焉。此教之为度。莫备于斯。而视诸古昔。不可同年而论也审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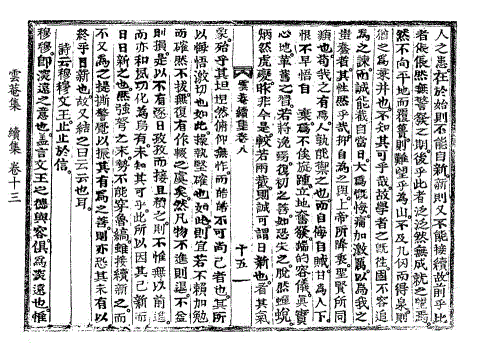 人之患。在于始则不能自新。新则又不能接续。故前乎比者伥伥然无警发之期。后乎此者泛泛然无成就之望焉。然不向平地而覆篑。则难望乎为山。不及九仞而得泉。则犹之为弃井也。不知其可乎哉。故学者之既往。固不容追为之谏。而诚能截自当日。大为慨悔。痛加激厉。以为我之蚩蠢者。其性然乎哉。抑自为之与。上帝所降衷。圣贤所同类也。苟我之有为。人孰能御之也。而自侮自贼。甘为人下。恨不早悟自 弃。为不俟旋踵。立地奋发。端的容仪。真实心地。革旧之习。若将浼焉。复初之善。如恐失之。脱然蝉蜕。炳然虎变。昨非今是。较若两截。则诚可谓日新也。看其气象。殆乎其坦坦然俯仰无怍。而皓皓不可尚已者也。其所以悔悟激切也如此。操执坚确也如此。则宜若不赖加勉而确然不拔。无复有作辍之虞矣。然凡物不进则退。不益则损。是以不有逐日孜孜而接且续之。则不惟无以前进。而亦和夙功化为乌有。未知其可乎。此所以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也。然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虽接续新之。而不又为之提撕警觉以振其有为之善。则亦恐其未有以终乎日新也。故又结之曰云云也耳。
人之患。在于始则不能自新。新则又不能接续。故前乎比者伥伥然无警发之期。后乎此者泛泛然无成就之望焉。然不向平地而覆篑。则难望乎为山。不及九仞而得泉。则犹之为弃井也。不知其可乎哉。故学者之既往。固不容追为之谏。而诚能截自当日。大为慨悔。痛加激厉。以为我之蚩蠢者。其性然乎哉。抑自为之与。上帝所降衷。圣贤所同类也。苟我之有为。人孰能御之也。而自侮自贼。甘为人下。恨不早悟自 弃。为不俟旋踵。立地奋发。端的容仪。真实心地。革旧之习。若将浼焉。复初之善。如恐失之。脱然蝉蜕。炳然虎变。昨非今是。较若两截。则诚可谓日新也。看其气象。殆乎其坦坦然俯仰无怍。而皓皓不可尚已者也。其所以悔悟激切也如此。操执坚确也如此。则宜若不赖加勉而确然不拔。无复有作辍之虞矣。然凡物不进则退。不益则损。是以不有逐日孜孜而接且续之。则不惟无以前进。而亦和夙功化为乌有。未知其可乎。此所以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也。然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虽接续新之。而不又为之提撕警觉以振其有为之善。则亦恐其未有以终乎日新也。故又结之曰云云也耳。诗云穆穆文王。止止于信。
穆穆。即深远之意也。盖言文王之德与容。俱为深远也。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7L 页
 其德容。俱为深远也。故其所以为至善之功。则接续不已而无一息之间。光明不昧而无一毫之疏焉。其所以为日用之验。则敬戒不怠而无一念之不慎。安于所止而无一物不得其所者也。此作诗者所以叹美文王。而总以穆穆称之也。然则缉熙。乃所以为敬止者也。而要其归宿则为在于敬止一句者审矣。然其言含畜。不为之发。则道不见矣。是以传之者从而释之曰云云。五者乃天下之至善。圣人之止。亦何加于此焉。盖君者统民庶而出治者也。不或视之如伤。则无以为君而民失所矣。其敢不以仁政为之自尽乎。此文王所以子视民庶而不遑朝食者也。臣者所以致身而事君者也。不或以舜之事尧事之。则无以为治而国亦随以危矣。敢不夙夜殚竭。求有以仰报万一乎。此文王所以率商叛国而服事者也。孝也者。事亲之本分也。为人子者。其敢不为尽心乎。如记之所谓为世子也。日三朝于王季者是也。慈也者。爱子之至情也。为人父者。其得不为之自致乎。如诗之所谓螽斯麟趾之化是也。信为圣人之大节。而其止也极。故如汉南四十馀国。信之如神明。而皆以为受命之君而无思不报。亦其一验也。然则文王之所以止至善者。不亦缉熙之至乎。不亦穆穆之盛乎哉。
其德容。俱为深远也。故其所以为至善之功。则接续不已而无一息之间。光明不昧而无一毫之疏焉。其所以为日用之验。则敬戒不怠而无一念之不慎。安于所止而无一物不得其所者也。此作诗者所以叹美文王。而总以穆穆称之也。然则缉熙。乃所以为敬止者也。而要其归宿则为在于敬止一句者审矣。然其言含畜。不为之发。则道不见矣。是以传之者从而释之曰云云。五者乃天下之至善。圣人之止。亦何加于此焉。盖君者统民庶而出治者也。不或视之如伤。则无以为君而民失所矣。其敢不以仁政为之自尽乎。此文王所以子视民庶而不遑朝食者也。臣者所以致身而事君者也。不或以舜之事尧事之。则无以为治而国亦随以危矣。敢不夙夜殚竭。求有以仰报万一乎。此文王所以率商叛国而服事者也。孝也者。事亲之本分也。为人子者。其敢不为尽心乎。如记之所谓为世子也。日三朝于王季者是也。慈也者。爱子之至情也。为人父者。其得不为之自致乎。如诗之所谓螽斯麟趾之化是也。信为圣人之大节。而其止也极。故如汉南四十馀国。信之如神明。而皆以为受命之君而无思不报。亦其一验也。然则文王之所以止至善者。不亦缉熙之至乎。不亦穆穆之盛乎哉。诗云于戏前王不忘。止没世不忘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8H 页
 于戏。盖叹辞也。而追夫前王之德巍巍盛大。有未能以言语尽之者。故作诗者为先发叹于此。而只以一言蔽之曰不忘。盖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然则不忘二字。大有蕴奥。而其义也含畜不露也。故传之者从而发之曰。乃圣乃神。王之所贤也。见乎羹墙而感戴之至也。膝我腹我。王之所亲也。陟降庭止而绍述之至也。绥之斯来。动之斯和。王之所乐利而天下后世之匹夫匹妇所以各获自尽者也。此前王之世虽已没。而君子小人。所以举皆服膺铭心而不容咽忘者也。
于戏。盖叹辞也。而追夫前王之德巍巍盛大。有未能以言语尽之者。故作诗者为先发叹于此。而只以一言蔽之曰不忘。盖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然则不忘二字。大有蕴奥。而其义也含畜不露也。故传之者从而发之曰。乃圣乃神。王之所贤也。见乎羹墙而感戴之至也。膝我腹我。王之所亲也。陟降庭止而绍述之至也。绥之斯来。动之斯和。王之所乐利而天下后世之匹夫匹妇所以各获自尽者也。此前王之世虽已没。而君子小人。所以举皆服膺铭心而不容咽忘者也。是以大学始教。止以求至乎其极。
夫知之未致。非心之无知。只为物之未格也。理之未尽。非物之无理。只为知之未致也。然则物之格与不格。独不在于知乎。知之致与不致。独不在于理乎。如是则格致。乃开卷第一义也。不知为大学者。将如何用力乎。夫天下之物。皆理之所散。而在我之心则知之理也。故学者必就天下之物。因我已知之理而穷诸物。则不患研究之无苗脉。而于推致。亦可一以贯之矣。但益穷二字。须着子细理会。盖已知之理。只为温旧而有限。渐知之理。便是解新而无穷也。故穷究者。必有以寻夫物理之所在。而自粗而精。自浅而深。千了百当。以至乎无复可穷。然后始谓物理之极处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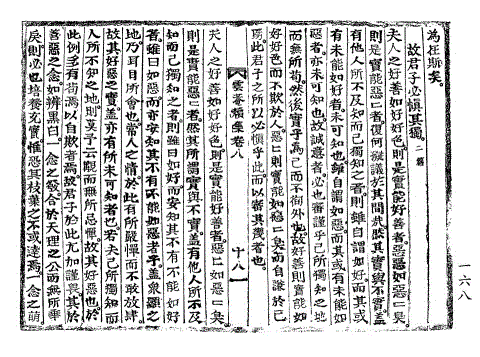 为在斯矣。
为在斯矣。故君子必慎其独。(二篇)
夫人之好善如好好色。则是实能好善者。恶恶如恶恶臭。则是实能恶恶者。复何拟议于其间哉。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则虽自谓如好。而其或有未能如好者。未可知也。虽自谓如恶。而其或有未能如恶者。亦未可知也。故诚意者。必也审谨乎己所独知之地而无所苟。然后实乎为己而不徇外也。故好善则实能如好好色而不欺于人。恶恶则实能如恶恶臭而自谦于己焉。此君子之所以必慎乎此。而以审其几者也。
夫人之好善如好好色。则是实能好善者。恶恶如恶恶臭。则是实能恶恶者。然其所谓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则虽曰如好。而安知其不有不能如好者。虽曰如恶。而亦安知其不有不能如恶者乎。盖众显之地。乃耳目所会也。常人之情。于此有所严惮而不敢放肆。故其好恶之实。盖亦有所未可知者也。若夫己所独知而人所不知之地。则莫予云觏而无所忌惮。故其好恶也。于此例多有苟焉以自欺者焉。故君子于此尤加谨畏。其于善恶之念。如辨黑白。一念之发。合于天理之公而无所乖戾。则必也培养充实。惟恐其枝叶之不或达焉。一念之萌。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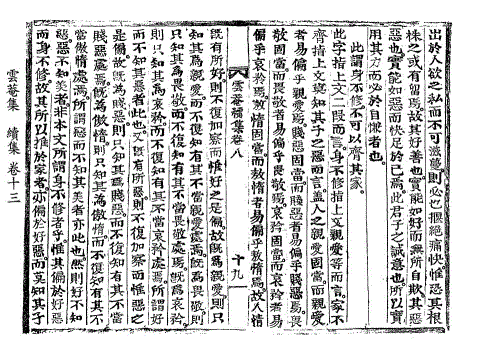 出于人欲之私而不可滋蔓。则必也揠绝痛快。惟恐其根株之或有留焉。故其好善也。实能如好而无所自欺。其恶恶也。实能如恶而快足于己焉。此君子之诚意也。所以实用其力而必于自慊者也。
出于人欲之私而不可滋蔓。则必也揠绝痛快。惟恐其根株之或有留焉。故其好善也。实能如好而无所自欺。其恶恶也。实能如恶而快足于己焉。此君子之诚意也。所以实用其力而必于自慊者也。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此字指上文二段而言。身不修指上文亲爱等而言。家不齐指上文莫知其子之恶而言。盖人之亲爱固当。而亲爱者易偏乎亲爱焉。贱恶固当。而贱恶者易偏乎贱恶焉。畏敬固当。而畏敬者易偏乎畏敬焉。哀矜固当。而哀矜者易偏乎哀矜焉。敖惰固当。而敖惰者易偏乎敖惰焉。故人情既有所好。则不复加察而惟好之是偏。故既为亲爱。则只知其为亲爱。而不复知有其不当亲爱处焉。既为畏敬。则只知其为畏敬。而不复知有其不当畏敬处焉。既为哀矜。则只知其为哀矜。而不复知有其不当哀矜处焉。所谓好而不知其恶者此也。又既有所恶。则不复加察而惟恶之是偏。故既为贱恶。则只知其为贱恶。而不复知有其不当贱恶处焉。既为傲惰。则只知其为傲惰。而不复知有其不当傲惰处焉。所谓恶而不知其美者亦此也。然则好不知恶。恶不知美者。非本文所谓身不修者乎。惟其偏于好恶而身不修。故其所以推于家者。亦偏于好恶。而莫知其子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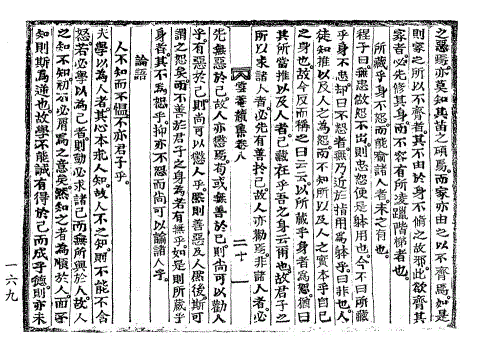 之恶焉。亦莫知其苗之硕焉。而家亦由之以不齐焉。如是则家之所以不齐者。其不由于身不脩之故邪。此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而不容有所凌躐阶梯者也。
之恶焉。亦莫知其苗之硕焉。而家亦由之以不齐焉。如是则家之所以不齐者。其不由于身不脩之故邪。此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而不容有所凌躐阶梯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程子曰。无忠做恕不出。则忠恕便是体用也。今不曰所藏乎身不忠。却曰不恕者。无乃近于指用为体乎。曰非也。人徒知推以及人之为恕。而不知所以及人之实本乎自己之身也。故今反而称之曰云云。以所藏乎身者为恕。犹曰其所当推以及人者。已藏在乎吾之身云尔也。故君子之所以求诸人者。必先有善于己。故人亦劝焉。非诸人者。必先无恶于己。故人亦惩焉。苟或无善于己。则尚可以劝人乎。有恶于己。则尚可以惩人乎。然则善恶及人然后。斯可谓之恕矣。而不善于君子之身为若有无乎。如是则所藏乎身者。其不为恕乎。抑亦不恕而尚可以谕诸人乎。
论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夫学以为人者。其心本求人知。故人不之知。则不能不含怒。若必学以为己者。则动必求诸己而无所与于人。故人之知不知。初不必屑为之意矣。然知之者为顺于人。而不知则斯为逆也。故学不能诚有得于己而成乎德。则亦未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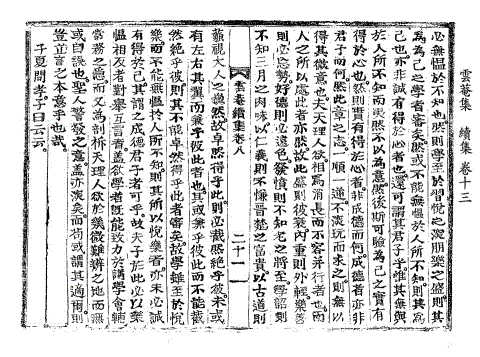 必无愠于不知也。然则学至于习悦之深朋乐之盛。则其为为己之学者审矣。然或不能无愠于人所不知。则其为己也。亦非诚有得于心者也。还可谓其君子乎。惟其无与于人所不知而夷然不以为意。然后斯可验为己之实有得于心也。然则实有得于心者。非成德而何。成德者亦非君子而何。然此章之志。一顺一逆。不深玩而求之。则无以得其微意也。夫天理人欲。相为消长而不容并行者也。而人之所以处此者亦然。故此盛则彼衰。内重则外轻。乐善则必忘势。好德则必远色。发愤则不知老之将至。学韶则不知三月之肉味。以仁义则不慊晋楚之富贵。以古道则藐视大人之巍然。故卓然得乎此。则必截然绝乎彼。未或有左右其翼而兼乎彼此者也。其或兼乎彼此而不能截然绝乎彼。则其不能卓然得乎此者审矣。故学虽至于悦乐。而不能无愠于人所不知。则其所以悦乐者。亦未必诚有得于己。其谓之成德君子者可乎。故夫子于此必以乐愠相反者对举互言者。盖欲学者既能致力于讲学会辅当务之急。而又为剖析天理人欲于几微难辨之地而无或自误也。圣人警发之意。盖亦深矣。而苟或谓其适尔。则岂立言之本意乎也哉。
必无愠于不知也。然则学至于习悦之深朋乐之盛。则其为为己之学者审矣。然或不能无愠于人所不知。则其为己也。亦非诚有得于心者也。还可谓其君子乎。惟其无与于人所不知而夷然不以为意。然后斯可验为己之实有得于心也。然则实有得于心者。非成德而何。成德者亦非君子而何。然此章之志。一顺一逆。不深玩而求之。则无以得其微意也。夫天理人欲。相为消长而不容并行者也。而人之所以处此者亦然。故此盛则彼衰。内重则外轻。乐善则必忘势。好德则必远色。发愤则不知老之将至。学韶则不知三月之肉味。以仁义则不慊晋楚之富贵。以古道则藐视大人之巍然。故卓然得乎此。则必截然绝乎彼。未或有左右其翼而兼乎彼此者也。其或兼乎彼此而不能截然绝乎彼。则其不能卓然得乎此者审矣。故学虽至于悦乐。而不能无愠于人所不知。则其所以悦乐者。亦未必诚有得于己。其谓之成德君子者可乎。故夫子于此必以乐愠相反者对举互言者。盖欲学者既能致力于讲学会辅当务之急。而又为剖析天理人欲于几微难辨之地而无或自误也。圣人警发之意。盖亦深矣。而苟或谓其适尔。则岂立言之本意乎也哉。子夏问孝。子曰云云。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0L 页
 盖色不可以伪为者也。必有深爱根于心然后。自有愉悦之色见于面焉。然则此必爱亲之深然后。其色也方是如此愉悦。此色之所以为难也。至于服劳奉养。只不过为奉亲之常事也。盖为其非精微之理也。智虽未明。而足能推度知之。亦非高远之行也。诚虽未及。而足以勉强为之也。是以苟或色之不能自然愉悦。而只以此服劳奉养二事为尚。则其足以为孝也哉。盖子夏之学。循蹈本于规矩谨严。而于远者大者。或有所未尽也。是以事亲之际。其能敬也如此。而深爱之色。或有所不足。故夫子以是警之。盖父母至亲也。爱不可以不深。父母至尊也。敬不可以不至。苟于爱敬之间。一有不至。则是事亲之道。皆有所未尽而均于不孝也夫。
盖色不可以伪为者也。必有深爱根于心然后。自有愉悦之色见于面焉。然则此必爱亲之深然后。其色也方是如此愉悦。此色之所以为难也。至于服劳奉养。只不过为奉亲之常事也。盖为其非精微之理也。智虽未明。而足能推度知之。亦非高远之行也。诚虽未及。而足以勉强为之也。是以苟或色之不能自然愉悦。而只以此服劳奉养二事为尚。则其足以为孝也哉。盖子夏之学。循蹈本于规矩谨严。而于远者大者。或有所未尽也。是以事亲之际。其能敬也如此。而深爱之色。或有所不足。故夫子以是警之。盖父母至亲也。爱不可以不深。父母至尊也。敬不可以不至。苟于爱敬之间。一有不至。则是事亲之道。皆有所未尽而均于不孝也夫。季路问事鬼神云云。
盖人鬼死生一理也。故能事人则能事鬼神。知生则可以知死而无复间隔之虞焉。然幽明始终之序则不可躐也。故不能事人于明。则亦不能事鬼神于幽。不原于有生之始。则亦不可反于有死之终焉。盖孝于亲也。爱而不忘。故祭之日。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忠于君也。进思退思。故祭之曰于戏前王不忘焉。苟非忠孝者。恶得以不忘于祭乎。顾今季路问事鬼神则是不能诚敬于人事之明。而先致祭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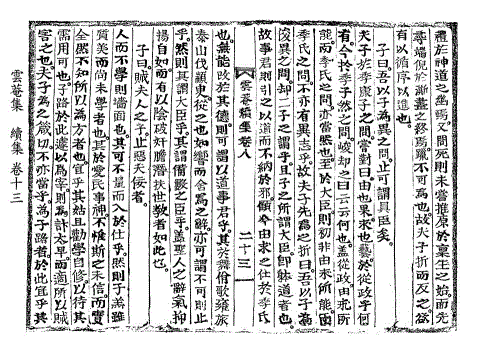 礼于神道之幽焉。又问死则未尝推原于禀生之始。而先寻端倪于澌尽之终焉。躐不可为也。故夫子折而反之。欲有以循序以进也。
礼于神道之幽焉。又问死则未尝推原于禀生之始。而先寻端倪于澌尽之终焉。躐不可为也。故夫子折而反之。欲有以循序以进也。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止可谓具臣矣。
夫子于季康子之问。尝对曰。由也果。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今于季子然之问。峻却之曰云云何也。盖从政。由求所能。而季氏之问。亦当然也。至于大臣。则初非由求所能。而季氏之问。不亦有异志乎。故夫子先为之折曰。吾以子为俊异之问。却二子之谓乎。且子之所谓大臣。即体道者也。故事君则引之以道而不纳于邪。顾今由求之仕于季氏也。无能改于其德。则可谓以道事君乎。其于舞佾歌雍旅泰山伐颛臾。从之也如响而舍为之辞。亦可谓不可则止乎。然则其谓大臣乎。其谓备数之臣乎。盖圣人之辞气抑扬自如。而有以阴破奸胆潜扶世教者如此也。
子曰。贼夫人之子。止恶夫佞者。
人而不学则墙面也。其可不量而入于仕乎。然则子羔虽质美而尚未学者也。其于爱民事神。不惟斯之未信。而实全然不知所以为方者也。宜乎其姑且劝学自修。以待其需用可也。子路于此遽以为宰。则为计太早。而适所以贼害之也。夫子为之箴切。不亦当乎。为子路者。于此宜乎其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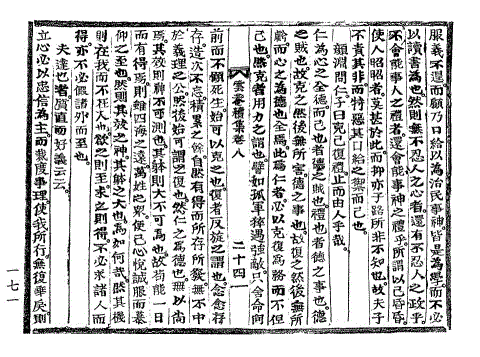 服义不遑。而顾乃口给以为治民事神。皆是为学。而不必以读书为也。然则无不忍人之心者。还有不忍人之政乎。不会能事人之礼者。还会能事神之礼乎。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莫甚于此。而抑亦子路所非不知也。故夫子不责其非。而特恶其口给之御而已也。
服义不遑。而顾乃口给以为治民事神。皆是为学。而不必以读书为也。然则无不忍人之心者。还有不忍人之政乎。不会能事人之礼者。还会能事神之礼乎。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莫甚于此。而抑亦子路所非不知也。故夫子不责其非。而特恶其口给之御而已也。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止而由人乎哉。
仁为心之全德。而己也者德之贼也。礼也者德之事也。德之贼也。故克之然后无所害。德之事也。故复之然后无所亏。而心之为德也全焉。此为仁者。必以克复为务而不但已也。然克者用力之谓也。譬如孤军猝遇强敌。只舍命向前而不顾死生。始可以克之也。复者反旋之谓也。念念存存。造次不忘。积累之馀。自然有得而所存所发。无不中于义理之公。然后始可谓之复也。然仁之为德也。无以尚焉。其效则神不可测也。其体则大不可为也。故苟能一日而有得焉。则虽四海之远。万姓之众。便已心悦诚服而慕仰之至也。然则其效之神。其体之大也。为如何哉。然其机则在我而不在人也。欲之则至。求之则得。不必求诸人而得。亦不必假诸外而至也。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云云。
立心必以忠信为主。而裁度事理。使我所行。无复乖戾。则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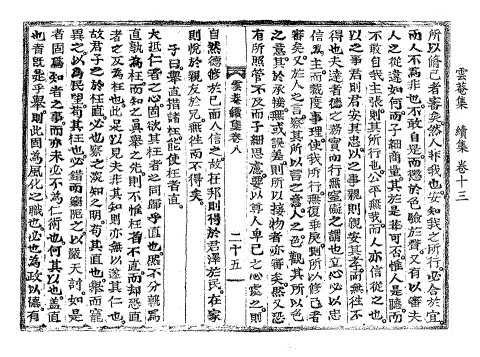 所以脩己者审矣。然人非我也。安知我之所行。必合于宜。而人不为非也。不敢自是。而惩于色验于声。又有以审夫人之从违如何。而子细商量。其于是非可否。惟人是听。而不敢自我主张。则其所行也。公平无我。而人亦信从之也。以之事君则君安其忠。以之事亲则亲安其孝。而无往不得也夫达者德之务实而行无窒碍之谓也立心必以忠信为主。而裁度事理。使我所行。无复乖戾。则所以修己者审矣。又于人之言。察其所以言之意。人之。色观其所以色之意。其于承接。无或误差。则所以接物者亦审矣。然又恐有所照管不及而子细思虑。要以尊人卑己之心处之。则自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故在邦则得于君泽于民。在家则悦于亲友于兄。无往而不得矣。
所以脩己者审矣。然人非我也。安知我之所行。必合于宜。而人不为非也。不敢自是。而惩于色验于声。又有以审夫人之从违如何。而子细商量。其于是非可否。惟人是听。而不敢自我主张。则其所行也。公平无我。而人亦信从之也。以之事君则君安其忠。以之事亲则亲安其孝。而无往不得也夫达者德之务实而行无窒碍之谓也立心必以忠信为主。而裁度事理。使我所行。无复乖戾。则所以修己者审矣。又于人之言。察其所以言之意。人之。色观其所以色之意。其于承接。无或误差。则所以接物者亦审矣。然又恐有所照管不及而子细思虑。要以尊人卑己之心处之。则自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故在邦则得于君泽于民。在家则悦于亲友于兄。无往而不得矣。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
大抵仁者之心。固欲其枉者之同归乎直也。然不分孰为直孰为枉。而知之真举之先。则不惟枉者不直。而却恐直者之反为枉也。此足以见夫非其知则亦无以遂其仁也。故君子之于枉直。必也察之深知之明。苟其直也。举而宠异之。以为民望。苟其枉也。必错而穷阨之。以严天讨。如是者固为知者之事。而亦未必不为仁术也。何其以也。盖直也者既是乎举。则此固为风化之职也。必也为政以德。有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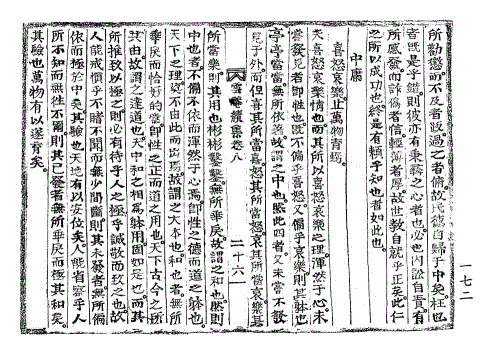 所劝惩。而不及者跂。过之者俯。故民德自归于中矣。枉也者既是乎错。则彼亦有秉彝之心者也。必也内讼自责。有所感发。而诈伪者信。轻薄者厚。故世教自就乎正矣。此仁之所以成功也。终是有赖乎知也者如此也。
所劝惩。而不及者跂。过之者俯。故民德自归于中矣。枉也者既是乎错。则彼亦有秉彝之心者也。必也内讼自责。有所感发。而诈伪者信。轻薄者厚。故世教自就乎正矣。此仁之所以成功也。终是有赖乎知也者如此也。中庸
喜怒哀乐。止万物育焉。
夫喜怒哀乐情也。而其所以喜怒哀乐之理。浑然于心。未尝发见者即性也。既不偏乎喜怒。又偏乎哀乐。则其体也亭亭当当。无所依著。故谓之中也。然此四者。又未尝不发见于外。而但喜其所当喜。怒其所当怒。哀其所当哀。乐其所当乐。则其用也彬彬凿凿。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也。然则中也者。不偏不依而浑然于心焉。即性之德而道之体也。天下之理。莫不由此而出焉。故谓之大本也。和也者。无所乖戾而恰好的当。即性之正而道之用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谓之达道也。夫中和之相为体用。固如是也。而其所推致以极之。则必有待乎人之极乎诚敬而致之也。故人能戒慎乎不睹不闻而无少间断。则其未发者。无所偏依而极于中矣。其验也天地有以安位矣。人能省察乎人所不知而无往不尔。则其已发者无所乖戾而极其和矣。其验也万物有以遂育矣。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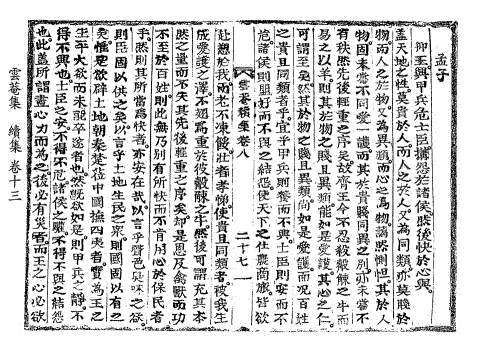 孟子
孟子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搆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盖天地之性。莫贵于人。而人之于人。又为同类。亦莫贱于物。而人之于物。又为异类。而心之为物。蔼然恻怛。其于人物。固未尝不同爱一护。而其于贵贱同异之别。亦未尝不有秩然先后轻重之序矣。故齐王今不忍杀觳觫之牛而易之以羊。则其于物之贱且异类。能如是爱护。其心之仁。可谓至矣。然其于物之贱且异类。尚如是爱护。而况百姓之贵且同类者乎。宜乎甲兵则养而不兴。士臣则安而不危。诸侯则盟好而不与之结怨。使天下之仕农商旅。皆欲赴愬于我。而老不冻馁。壮者孝悌。使贵且同类者。被我生成爱护之泽。不翅为重于彼觳觫之牛。然后可谓充其本然之量而不失其先后轻重之序矣。却是恩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则此无乃别有所快而不肯用心于保民者乎。然则其所当为快者。亦安在哉。以言乎声色臭味之欲。则臣固以供之矣。以言乎土地生民之众。则国固以有之矣。惟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抚四夷者。实为王之生平大欲而未能卒遂者也。然既欲如是。则甲兵之静。不得不兴也。士臣之安。不得不危。诸侯之驩。不得不与之结怨也。此盖所谓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者。而王之心必欲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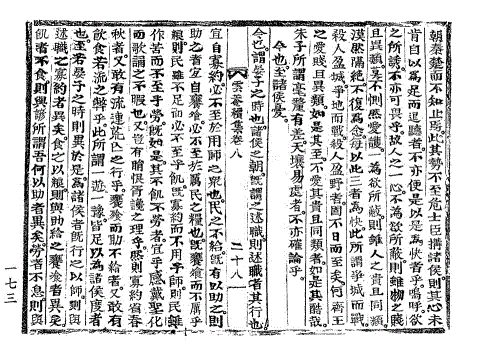 朝秦楚而不知止焉。此其势不至危士臣搆诸侯。则其心未肯自以为足而退听者。不亦便是以是为快者乎。呜呼。欲之所诱。不亦可畏乎。故人之一心。不为欲所蔽。则虽物之贱且异类。莫不恻然爱护。一为欲所蔽。则虽人之贵且同类漠然隔绝。不复为念。每以此三者为快。此所谓争城而战。杀人盈城。争地而战。杀人盈野者。固不日而至矣。何齐王之爱贱且异类。如是其至。不爱其贵且同类者。如是其酷哉。朱子所谓毫釐有差。天壤易处者。不亦确论乎。
朝秦楚而不知止焉。此其势不至危士臣搆诸侯。则其心未肯自以为足而退听者。不亦便是以是为快者乎。呜呼。欲之所诱。不亦可畏乎。故人之一心。不为欲所蔽。则虽物之贱且异类。莫不恻然爱护。一为欲所蔽。则虽人之贵且同类漠然隔绝。不复为念。每以此三者为快。此所谓争城而战。杀人盈城。争地而战。杀人盈野者。固不日而至矣。何齐王之爱贱且异类。如是其至。不爱其贵且同类者。如是其酷哉。朱子所谓毫釐有差。天壤易处者。不亦确论乎。今也。至诸侯忧。
今也。谓晏子之时也。诸侯之朝。既谓之述职。则述职者其行也。宜自寡约。必不至于用师之众也。民之不给。既有以助之。则助之者宜自饔飧。必不至于厉民之粮也。既饔飧而不厉乎粮。则民虽不足而必不至乎饥。既寡约而不用乎师。则民虽作苦而不至乎劳。既如是。其不饥不劳者。宜乎感戴圣化而歌诵之不暇也。又岂有睊恨胥谗之理乎。然则寡约省春秋者。又敢有流连荒亡之行乎。饔飧而助不给者。又敢有饮食若流之弊乎。此所谓一游一豫。皆足以为诸侯度者也。至若晏子之时则异于是。为诸侯者既行之以师。则与述职之寡约者异矣。食之以粮。则与助给之饔餐者异矣。饥者不食。则与谚所谓吾何以助者异矣。劳者不息。则与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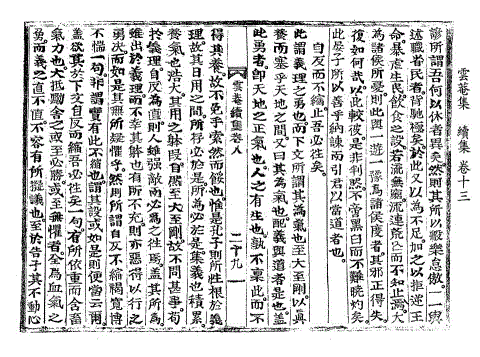 谚所谓吾何以休者异矣。然则其所以般乐怠傲。一一与述职省民者。背驰极矣。于此又以为不足。加之以拒逆王命。暴虐生民。饮食之设。若流无穷。流连荒亡而不知止焉。大为诸侯所忧。则此与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者。其邪正得失。复如何哉。以此较彼。是非判然。不啻黑白而不难晓灼矣。此晏子所以善乎纳谏而引君以当道者也。
谚所谓吾何以休者异矣。然则其所以般乐怠傲。一一与述职省民者。背驰极矣。于此又以为不足。加之以拒逆王命。暴虐生民。饮食之设。若流无穷。流连荒亡而不知止焉。大为诸侯所忧。则此与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者。其邪正得失。复如何哉。以此较彼。是非判然。不啻黑白而不难晓灼矣。此晏子所以善乎纳谏而引君以当道者也。自反而不缩。止吾必往矣。
此谓义理之勇也。而下文所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真养而塞乎天地之间。又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者是也。盖此勇者。即天地之正气也。人之有生也。孰不禀此。而不得其养。故不免乎索然而馁也。惟是孔子则所性根于义理。故其日用之间。所存必于是。所为必于是。集义也积累。养气也浩大。其用之体段。自然至大至刚。故不问甚事。苟于义理。自反为直。则人虽强敌而必为之往焉。盖其所为。虽出于义理。而不幸其体也有所不充。则亦恶得以行之勇决。而如是其无所疑惧乎。然则所谓自反不缩褐宽博不惴一句。非谓实有此不缩也。谓其设或如是则便当云尔。盖欲其于下文自反而缩吾必往矣一句。有所依重而含畜气力也。大抵黝舍之或至必胜。或至无惧者。全为血气之勇。而义之直不直。不容有所拟议也。至于告子其不动心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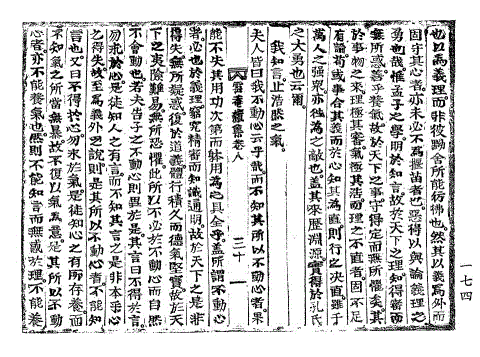 也以为义理。而非彼黝舍所能彷佛也。然其以义为外而固守其心者。亦未必不为揠苗者也。恶得以与论义理之勇也哉。惟孟子之学。明于知言。故于天下之理。知得审而无所惑。善乎养气。故于天下之事。守得定而无所惧矣。其于事物之来。理极其审。气极其浩。而理之不直者。固不足有论。苟或事合其义而于心知其为直。则行之决直。虽千万人之强众。亦往为之敌也。盖其来历渊源。实得于孔氏之大勇也云尔。
也以为义理。而非彼黝舍所能彷佛也。然其以义为外而固守其心者。亦未必不为揠苗者也。恶得以与论义理之勇也哉。惟孟子之学。明于知言。故于天下之理。知得审而无所惑。善乎养气。故于天下之事。守得定而无所惧矣。其于事物之来。理极其审。气极其浩。而理之不直者。固不足有论。苟或事合其义而于心知其为直。则行之决直。虽千万人之强众。亦往为之敌也。盖其来历渊源。实得于孔氏之大勇也云尔。我知言。止浩然之气。
夫人皆曰我不动心云乎哉。而不知其所以不动心者。果能不失其用功次第而体用为之具全乎。盖所谓不动心者。必也于义理。穷究精审而知识通明。故于天下之是非得失。无所疑惑。复于道义。体行积久而德气坚实。故于天下之夷险难易。无所恐惧。此所以不必于不动心而自然不会动也。若夫告子之不动心则异于是。其言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徒知人之有言。而不知其言之是非本乎心之得失。故至为义外之说。则是其所以不动心者。不能知言也。又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徒知心之有所存养。而不知气之所当无暴。故不复以气为意。是其所以不动心者。亦不能养气也。然则不能知言而无惑于理。不能养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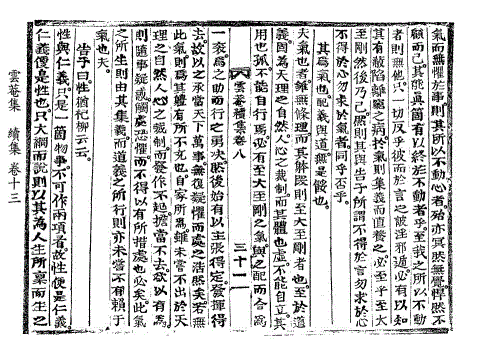 气而无惧于事。则其所以不动心者。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其能真个有以终于不动者乎。至我之所以不动者则无他。只一切反乎彼而于言之诐淫邪遁。必有以知其有蔽陷离穷之病。于气则集义而直养之。必至乎至大至刚然后乃已。然则其与告子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同乎否乎。
气而无惧于事。则其所以不动心者。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其能真个有以终于不动者乎。至我之所以不动者则无他。只一切反乎彼而于言之诐淫邪遁。必有以知其有蔽陷离穷之病。于气则集义而直养之。必至乎至大至刚然后乃已。然则其与告子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者。同乎否乎。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夫气也者。虽无条理。而其体段则至大至刚者也。至于道义。固为天理之自然。人心之裁制。而其体也虚。不能自立。其用也孤。不能自行焉。必有至大至刚之气。与之配而合为一衮。为之助而行之勇决。然后始有以主张得定。发挥得去。故以之承当天下万事。无复疑惧而处之浩然矣。若无此气。则为其体有所不充也。自家所为。虽未尝不出于天理之自然人心之裁制。而发作不起。担当不去。欲以有为。则随事疑惑。触处恐惧。而不得以有所措处也必矣。此气之所生则由其集义。而道义之所行则亦未尝不有赖于气也夫。
告子曰。性犹杞柳云云。
性与仁义。只是一个物事。不可作两项看。故性便是仁义。仁义便是性也。只大纲而说则以其为人生所禀而生之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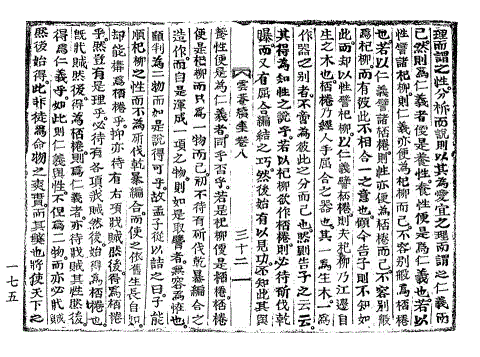 理而谓之性。分析而说则以其为爱宜之理而谓之仁义而已。然则为仁义者便是养性。养性便是为仁义也。若以性譬诸杞柳。则仁义亦便为杞柳而已。不容别般为杯棬也。若以仁义譬诸杯棬。则性亦便为杯棬而已。不容别般为杞柳。而有彼此不相合一之意也。顾今告子则不知如此。而却以性譬杞柳。以仁义譬杯棬。则夫杞柳乃江边自生之木也。杯棬乃经人手屈合之器也。其一为生木。一为作器之别者。不啻为彼此之分而已也。然则告子之云云。其得为知性之说乎。若以杞柳欲作杯棬。则必待斫伐乾曝。而又有屈合编结之巧。然后始有以见功。不知此其与养性便是为仁义者。同乎否乎。若是杞柳便是杯棬。杯棬便是杞柳而只为一物而已。初不待有斫伐乾暴编合之造作。而自是浑成一项之物。则如是取譬者。无容为怪也。顾判为二物而如是说得可乎。故孟子从以诘之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不为斫伐乾暴编合。而使之依旧生长自如。却能搆为杯棬乎。抑亦待有右项戕贼然后。得为杯棬乎。然岂有是理乎。必待有各项戕贼然后。始得为杯棬也。既戕贼然后。得为杯棬。则为仁义者。亦待戕贼其性然后。得为仁义乎。如此则仁义与性。不但为二物。而亦必戕贼然后始得。此非徒为命物之爽实。而其弊也将使天下之
理而谓之性。分析而说则以其为爱宜之理而谓之仁义而已。然则为仁义者便是养性。养性便是为仁义也。若以性譬诸杞柳。则仁义亦便为杞柳而已。不容别般为杯棬也。若以仁义譬诸杯棬。则性亦便为杯棬而已。不容别般为杞柳。而有彼此不相合一之意也。顾今告子则不知如此。而却以性譬杞柳。以仁义譬杯棬。则夫杞柳乃江边自生之木也。杯棬乃经人手屈合之器也。其一为生木。一为作器之别者。不啻为彼此之分而已也。然则告子之云云。其得为知性之说乎。若以杞柳欲作杯棬。则必待斫伐乾曝。而又有屈合编结之巧。然后始有以见功。不知此其与养性便是为仁义者。同乎否乎。若是杞柳便是杯棬。杯棬便是杞柳而只为一物而已。初不待有斫伐乾暴编合之造作。而自是浑成一项之物。则如是取譬者。无容为怪也。顾判为二物而如是说得可乎。故孟子从以诘之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不为斫伐乾暴编合。而使之依旧生长自如。却能搆为杯棬乎。抑亦待有右项戕贼然后。得为杯棬乎。然岂有是理乎。必待有各项戕贼然后。始得为杯棬也。既戕贼然后。得为杯棬。则为仁义者。亦待戕贼其性然后。得为仁义乎。如此则仁义与性。不但为二物。而亦必戕贼然后始得。此非徒为命物之爽实。而其弊也将使天下之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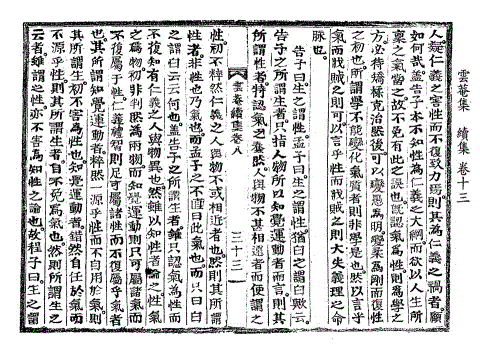 人。疑仁义之害性而不复致力焉。则其为仁义之祸者。顾如何哉。盖告子本不知性为仁义之大纲。而欲以人生所禀之气当之。故不免有此之误也。既认气为性。则为学之方。必待矫楺克治然后。可以变愚为明。变柔为刚而复性之初也。所谓学不能变化气质者则非学是也。然以言乎气而戕贼之则可。以言乎性而戕贼之则大失义理之命脉也。
人。疑仁义之害性而不复致力焉。则其为仁义之祸者。顾如何哉。盖告子本不知性为仁义之大纲。而欲以人生所禀之气当之。故不免有此之误也。既认气为性。则为学之方。必待矫楺克治然后。可以变愚为明。变柔为刚而复性之初也。所谓学不能变化气质者则非学是也。然以言乎气而戕贼之则可。以言乎性而戕贼之则大失义理之命脉也。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欤云。
告子之所谓生者。只指人物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则其所谓性者。特认气之蠢然。人与物不甚相远者而便谓之性。初不粹然仁义之人与物不或相近者也。然则其所谓性者。非性也乃气也。而孟子之不直曰此气也。而只曰白之谓白云云何也。盖告子之所谓生者。虽只认气为性而不复知有仁义之人与物异也。然虽以知性者论之。性气之为物。初非判然为两物。而知觉运动则只可属诸气而不复属于性。仁义礼智则足可属诸性而不复属乎气者也。其所谓知觉运动者。粹然一源乎性而不自用于气。则其所谓生。初不害为性也。知觉运动者。错然自任于气而不源乎性。则其所谓生者。自不免为气也。然则所谓生之云者。虽谓之性。亦不害为知性之论也。故程子曰。生之谓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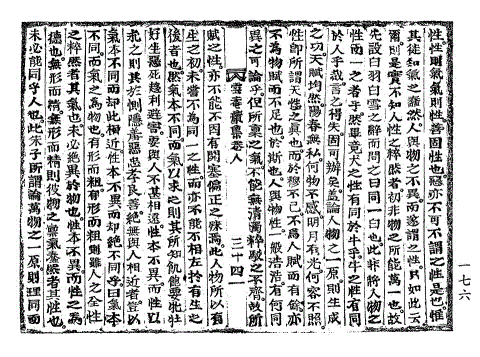 性。性则气气则性。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也。惟其徒知气之蠢然。人与物之不异。而遂谓之性。只如此云尔。则是实不知人性之粹然者。初非物之所能万一也。故先设白羽白雪之辞而问之曰同一白也。此非将人物之性而一之者乎。然毕竟犬之性有同于牛乎。牛之性有同于人乎哉。言之得失。固可办矣。盖论人物之一原。则生成之功。天赋均然。阳春无私。何物不感。明月有光。何容不照。性即所谓天性之真也。而于穆不已。不为人赋而有馀。亦不为物赋而不足也。于斯也。人与物性。一般浩浩。有何同异之可论乎。但所禀之气。不能无清浊粹驳之不齐。故所赋之性。亦不能不因有开塞偏正之殊焉。此人物所以有生之初。未尝不为同一之性。而亦不能不相左于有生之后者也。然气本不同。而气以求之则其所知饥饱要牝牡好生恶死趍利避害。要与人不甚相远。性本不异。而性以求之则其于恻隐羞恶忠孝良善。绝无与人相近者。岂以气本不同而却此相近。性本不异而却绝不同乎。曰气本不同。而气之为物也。有形而粗。有形而粗则虽人之全性之粹然者其气也。未必绝异于物也。性本不异。而性之为德也。无形而精。无形而精则彼物之禀气蠢然者其性也。未必能同乎人也。此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
性。性则气气则性。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也。惟其徒知气之蠢然。人与物之不异。而遂谓之性。只如此云尔。则是实不知人性之粹然者。初非物之所能万一也。故先设白羽白雪之辞而问之曰同一白也。此非将人物之性而一之者乎。然毕竟犬之性有同于牛乎。牛之性有同于人乎哉。言之得失。固可办矣。盖论人物之一原。则生成之功。天赋均然。阳春无私。何物不感。明月有光。何容不照。性即所谓天性之真也。而于穆不已。不为人赋而有馀。亦不为物赋而不足也。于斯也。人与物性。一般浩浩。有何同异之可论乎。但所禀之气。不能无清浊粹驳之不齐。故所赋之性。亦不能不因有开塞偏正之殊焉。此人物所以有生之初。未尝不为同一之性。而亦不能不相左于有生之后者也。然气本不同。而气以求之则其所知饥饱要牝牡好生恶死趍利避害。要与人不甚相远。性本不异。而性以求之则其于恻隐羞恶忠孝良善。绝无与人相近者。岂以气本不同而却此相近。性本不异而却绝不同乎。曰气本不同。而气之为物也。有形而粗。有形而粗则虽人之全性之粹然者其气也。未必绝异于物也。性本不异。而性之为德也。无形而精。无形而精则彼物之禀气蠢然者其性也。未必能同乎人也。此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7H 页
 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似而理绝不同者也。而彼告子则初昧乎性气之分。而直指气为性则犹之乎气即理理即气也。姑任之者未为不厚。而及至人物性之无分则甚矣。不得不为之辨也。然尚恨是时未有气质性之论也。未能为之撞破其性气合一也乎。
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似而理绝不同者也。而彼告子则初昧乎性气之分。而直指气为性则犹之乎气即理理即气也。姑任之者未为不厚。而及至人物性之无分则甚矣。不得不为之辨也。然尚恨是时未有气质性之论也。未能为之撞破其性气合一也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云云。
性即仁义礼智之根于心而不待外求者也。既仁义礼智之为性。则性之本善。其可诬乎。既不待外求。则求则得之者。不亦审乎。凡人不知性之为仁义礼智。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故以为性本不善而必待矫楺而后。可至仁义。此即外求之说也。不亦殊乎。盖自一原而论之。则天降生民。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则性之本善。固已昭然矣。然天下之言性。必以故为主者。盖故即已然之迹也。故语性之本然。则非但言者无据。亦听者之难必乎信。语其已然。则非但言者亲切。亦听者之无惑乎说也。然则仁义礼智。即性之本然也。孟子非不欲提缀示人。而浑然未发。未有端倪。则使发明甚至。其奈听者之未喻何。此孟子槩以性善晓告世人。而公都子之所不免疑问者也。然则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即所谓性之已然也。苟执此而晓告。则所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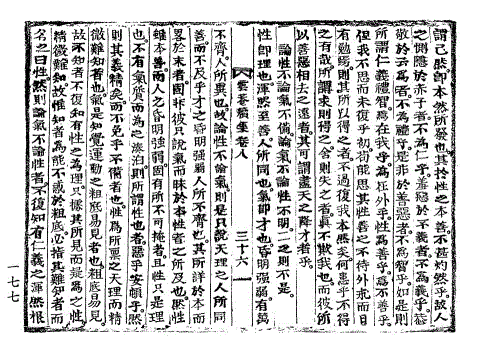 谓已然。即本然所发也。其于性之本善。不甚灼然乎。故人之恻隐于赤子者。不为仁乎。羞恶于不义者。不为义乎。恭敬于云为者。不为礼乎。是非于善恶者。不为智乎。如是则所谓仁义礼智。为在我乎。为在外乎。性为善乎。为不善乎。但我不思而未复乎初。苟能思其性善之不待外求而日有勉焉。则其所以得之者。不过复我本然矣。何患乎不得之有哉。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者。真不欺我也。而彼所以善恶相去之远者。其可谓尽天之降才者乎。
谓已然。即本然所发也。其于性之本善。不甚灼然乎。故人之恻隐于赤子者。不为仁乎。羞恶于不义者。不为义乎。恭敬于云为者。不为礼乎。是非于善恶者。不为智乎。如是则所谓仁义礼智。为在我乎。为在外乎。性为善乎。为不善乎。但我不思而未复乎初。苟能思其性善之不待外求而日有勉焉。则其所以得之者。不过复我本然矣。何患乎不得之有哉。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者。真不欺我也。而彼所以善恶相去之远者。其可谓尽天之降才者乎。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
性即理也。浑然至善。人所同也。气即才也。昏明强弱。有万不齐。人所异也。故论性不论气。则是只说天理之人所同善。而不及乎才之昏明强弱人所不齐也。其所详于本而略于末者。固非彼只说气而昧于本性者之所及也。然性虽本善。而人之昏明强弱。固有所不可掩者。且性只是理也。不有气质而为之凑泊。则所谓性也者。恶乎安顿乎。然则其义精矣。而不免乎不备者也。性为所禀之天理而精微难知者也。气是知觉运动之粗底易见者也。粗底易见。故不知者不复知有性之为理。只据其所见而疑为之性。精微难知。故惟知者为能不惑于粗底。必指其难知者而名之曰性。然则论气不论性者。不复知有仁义之浑然根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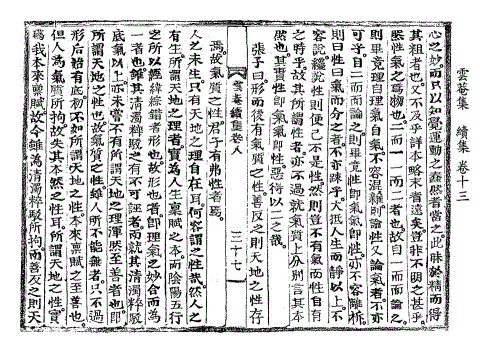 心之妙。而只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当之。此昧于精而得其粗者也。又不及乎详本略末者远矣。岂非不明之甚乎。然性气之为物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故自一而而论之。则毕竟理自理气自气。不容混杂。则论性又论气者。不亦可乎。自二而而论之。则毕竟性即气气即性。亦不容离析。则曰性曰气而分之者。不亦疏乎。大抵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则便已不是性。然则岂不有气而性自有之时乎。故其所谓性者。亦不过就气质上分别言其本然也。其实性即气气即性。恶得以二之哉。
心之妙。而只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当之。此昧于精而得其粗者也。又不及乎详本略末者远矣。岂非不明之甚乎。然性气之为物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故自一而而论之。则毕竟理自理气自气。不容混杂。则论性又论气者。不亦可乎。自二而而论之。则毕竟性即气气即性。亦不容离析。则曰性曰气而分之者。不亦疏乎。大抵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则便已不是性。然则岂不有气而性自有之时乎。故其所谓性者。亦不过就气质上分别言其本然也。其实性即气气即性。恶得以二之哉。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未生。只有天地之理自在耳。何容谓之性哉。然人之有生。所谓天地之理者。实为人生禀赋之本。而阴阳五行之所以经纬综错者形也。故形也者。即理气之妙合而为一者也。虽其清浊粹驳之有不可诬者。而就其清浊粹驳底气以上。亦未尝不有所谓天地之理浑然至善者也。即所谓天地之性也。故气质之性。虽人所不能无者。只不过形后始有底。初不如所谓天地之性。本来禀赋之至善也。但人为气质所拘。故失其本然之性耳。所谓天地之性。实为我本来禀赋。故今虽为清浊粹驳所拘。而善反之则天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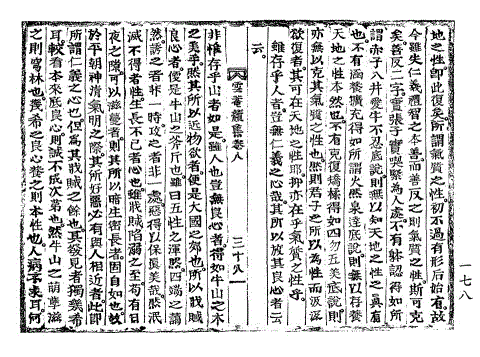 地之性。即此复矣。所谓气质之性。初不过有形后始有。故今虽失仁义礼智之本善。而善反之则气质之性。斯可克矣。善反二字。实张子实吃紧为人处。不有体认得如所谓赤子入井爱牛不忍底说。则无以知天地之性之真有也。不有涵养扩充得如所谓火然泉达底说。则无以存养天地之性本然也。不有克复矫楺得如四勿五美底说。则亦无以克其气质之性也。然则君子之所以为性而汲汲欲复者。其可在天地之性耶。抑亦在乎气质之性乎。
地之性。即此复矣。所谓气质之性。初不过有形后始有。故今虽失仁义礼智之本善。而善反之则气质之性。斯可克矣。善反二字。实张子实吃紧为人处。不有体认得如所谓赤子入井爱牛不忍底说。则无以知天地之性之真有也。不有涵养扩充得如所谓火然泉达底说。则无以存养天地之性本然也。不有克复矫楺得如四勿五美底说。则亦无以克其气质之性也。然则君子之所以为性而汲汲欲复者。其可在天地之性耶。抑亦在乎气质之性乎。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云云。
非惟存乎山者如是。虽人也岂无良心者。得如牛山之木之美乎。然其所以近物欲者。便是大国之郊也。所以戕贼良心者。便是牛山之斧斤也。虽曰五性之浑然。四端之蔼然。诱之者非一时。攻之者非一处。恶得以保真美哉。然泯灭不得者性。生长不已者心也。虽戕贼陷溺之至。苟有日夜之隙。可以滋蔓者。则其所以暗生密长者。固自如也。故于平朝神清气明之际。其所好恶必有与人相近者。此即所谓仁义之心也。但为其戕贼之馀也。其发见者独几希耳。较看本来底良心。则诚不成次第也。然牛山之萌孽滋之则穹林也。几希之良心养之则本性也。人病不求耳。何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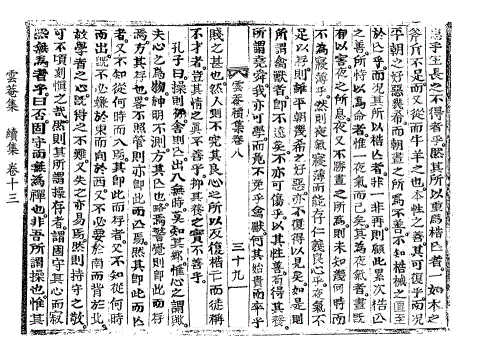 患乎生长之不得者乎。然其所以重为梏亡者。一如木之斧斤不足。而又从而牛羊之也。本性之善。其可复乎。而况平朝之好恶几希。而朝昼之所为不善。不知梏械之直至于亡乎。而况其所以梏亡者。非一非再。则顾此累次梏亡之善。所恃以为命者。惟一夜气而已矣。其为夜气者。昼既有以害。夜之所息。夜又不胜昼之所为。则未知几何时而不为寝薄乎。然则夜气寝薄而能存仁义良心乎。夜气不足以存。则虽平朝几希之好恶。亦不复得以见矣。如是则所谓禽兽者。即不远矣。不亦可伤乎。以其性善。苟得其养。所谓尧舜。我亦可学。而竟不免乎禽兽。何其始贵而卒乎贱之甚也。然人则不究其良心之所以反复梏亡而徒称不才者。岂其情之真不善乎。抑其养之实不善乎。
患乎生长之不得者乎。然其所以重为梏亡者。一如木之斧斤不足。而又从而牛羊之也。本性之善。其可复乎。而况平朝之好恶几希。而朝昼之所为不善。不知梏械之直至于亡乎。而况其所以梏亡者。非一非再。则顾此累次梏亡之善。所恃以为命者。惟一夜气而已矣。其为夜气者。昼既有以害。夜之所息。夜又不胜昼之所为。则未知几何时而不为寝薄乎。然则夜气寝薄而能存仁义良心乎。夜气不足以存。则虽平朝几希之好恶。亦不复得以见矣。如是则所谓禽兽者。即不远矣。不亦可伤乎。以其性善。苟得其养。所谓尧舜。我亦可学。而竟不免乎禽兽。何其始贵而卒乎贱之甚也。然人则不究其良心之所以反复梏亡而徒称不才者。岂其情之真不善乎。抑其养之实不善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
夫心之为物。神明不测。方其亡也。略焉警觉则即此而存焉。方其存也。略不照管则亦即此而亡焉。然其即此而亡者。又不知从何时而入焉。其即此而存者。又不知从何时而出。既不必嫌于东而向于西。又不必要于南而背于北。故学者之心。既得之不难。又失之亦易焉。然则持守之敬。可不顷刻慎之哉。然则其所谓操存者。谓固守其心而寂然无为者乎。曰否。固守而无为禅也。非吾所谓操也。惟其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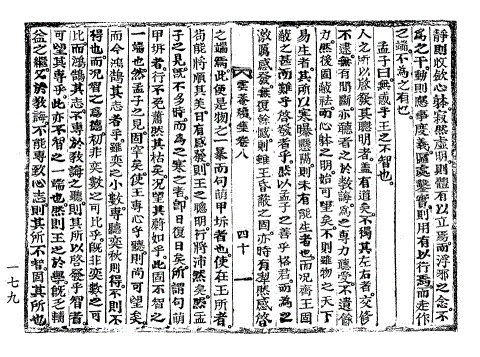 静则收敛心体。寂然虚明。则体有以立焉。而浮邪之念。不为之干。动则应事度义。区处凿实。则用有以行焉。而走作之端。不为之有也。
静则收敛心体。寂然虚明。则体有以立焉。而浮邪之念。不为之干。动则应事度义。区处凿实。则用有以行焉。而走作之端。不为之有也。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
人之所以启发其聪明者。盖有道矣。不独其左右者。交修不逮。无有间断。亦听者之于教诲。为之专力听受。不遗馀力。然后固蔽祛。而心体之明。始可望矣。不则虽物之天下易生者。其所以寒曝悬隔。则未有能生者也。而况齐王固蔽之甚而难乎启发者乎。然以孟子之善乎格君。而为之激厉感发。无复馀憾。则虽王昏蔽之固。亦时有犁然感启之端焉。此便是物之一暴而句萌甲坼者也。使在王所者。苟能将顺其美。日有感发。则王之聪明。行将沛然矣。然孟子之见。既不多时。而为之寒之者。即日复日矣。所谓句萌甲坼者。行不免萧然其枯矣。况望其蔚如乎。此固不智之一端也。然孟子之见。固罕矣。使王专心乎听。则尚可望矣。而今鸿鹄其志者乎。虽奕之小数。专听奕秋则得。不则不得也。而况智之为德。初非奕数之可比乎。既非奕数之可比。而鸿鹄其志。不专于教诲之听。则其所以启发乎智者。可望其专乎。此亦不智之一端也。然则王之于学。既乏辅益之继。又于教诲。不能专致心志。则其所不智。固其所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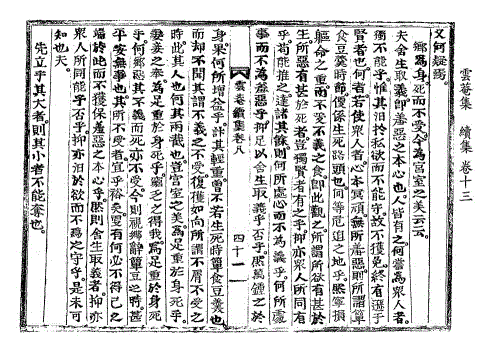 又何疑焉。
又何疑焉。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云云。
夫舍生取义。即羞恶之本心也。人皆有之。何尝为众人者。独不能乎。惟其汩于私欲而不能守。故不获免。终有逊于贤者也。何者。若使众人者。心本冥顽。无所羞恶。则所谓箪食豆羹时节。便系生死路头也。何等危迫之地乎。然宁损躯命之重。而不受不义之食。即此观之。所谓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独贤者有之乎。抑亦众人所同有乎。苟能推之。达诸其馀。则何所处心而不为义乎。何所处事而不为羞恶乎。抑足以舍生取义乎否乎。然万钟之于身。果何所增益乎。计其轻重。曾不若生死时箪食豆羹也。而却不闻其谓不义之不受。复获如向所谓不屑不受之时。此其人也何其两截也。岂宫室之美。为足重于身死乎。妻妾之奉。为足重于身死乎。穷乏之得我。为足重于身死乎。何乡恶其不义而死亦不受。今则视乡辞箪豆之时。甚平安无事也。其所不受者。宜乎裕矣。更有何必不得已之端于此而不获保羞恶之本心乎。然则舍生取义者。抑亦众人所同能乎否乎。抑亦汩于欲而不为之守乎。是未可知也夫。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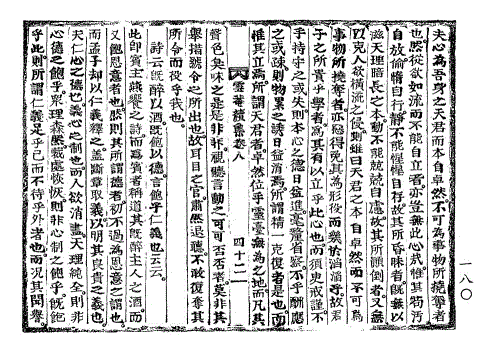 夫心为吾身之天君而本自卓然。不可为事物所挠夺者也。然从欲如流而不能自立者。亦岂无此心哉。惟其苟污自放。偷惰自行。静不能惺惺自存。故其所昏昧者。既无以滋天理暗长之本。动不能兢兢自虑。故其所颠倒者。又无以克人欲横流之侵。则虽曰天君之本自卓然而不可为事物所挠夺者。亦恶得免其为形役而几于滔滔乎。故君子之所贵乎学者。为其有以立乎此心也。而须臾戒谨。不乎持守之或失。则本心之德日益进。毫釐省察。不乎酬应之或疏。则物累之诱日益消焉。所谓精一克复者是也。而惟其立焉。所谓天君者。卓然位乎灵台无为之地。而凡其声色臭味之是是非非。视听言动之可可否否者。莫非其举措号令之所出也。故耳目之官。肃然退听。不敢复夺其所令而役乎我也。
夫心为吾身之天君而本自卓然。不可为事物所挠夺者也。然从欲如流而不能自立者。亦岂无此心哉。惟其苟污自放。偷惰自行。静不能惺惺自存。故其所昏昧者。既无以滋天理暗长之本。动不能兢兢自虑。故其所颠倒者。又无以克人欲横流之侵。则虽曰天君之本自卓然而不可为事物所挠夺者。亦恶得免其为形役而几于滔滔乎。故君子之所贵乎学者。为其有以立乎此心也。而须臾戒谨。不乎持守之或失。则本心之德日益进。毫釐省察。不乎酬应之或疏。则物累之诱日益消焉。所谓精一克复者是也。而惟其立焉。所谓天君者。卓然位乎灵台无为之地。而凡其声色臭味之是是非非。视听言动之可可否否者。莫非其举措号令之所出也。故耳目之官。肃然退听。不敢复夺其所令而役乎我也。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云云。
此即宾主燕飨之诗。而为宾者称道其既醉主人之酒。而又饱恩意者也。然则其所谓德者。初不过为恩意之谓也。而孟子却以仁义释之。盖断章取义。以明其良贵之义也。夫仁心之德也。义心之制也。而人欲消尽。天理纯全。则非心德之饱乎。众理森然。裁处恢恢。则非心制之饱乎。既饱乎此。则所谓仁义足乎己而不待乎外者也。而况其闻誉。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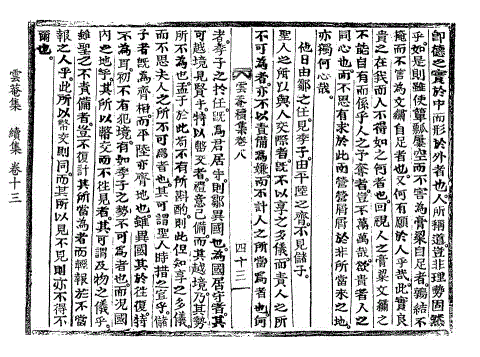 即德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也。人所称道。岂非理势固然乎。如是则虽使箪瓢屡空而不害为膏粱自足者。鹑结不掩而不害为文绣自足者也。又何有愿于人乎哉。此实良贵之在我而人不得如之何者也。回视人之膏粱文绣之不能自有而系乎人之予夺者。岂不万万哉。欲贵者人之同心也。而不思有求于此而营营屑屑于非所当求之地。亦独何心哉。
即德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也。人所称道。岂非理势固然乎。如是则虽使箪瓢屡空而不害为膏粱自足者。鹑结不掩而不害为文绣自足者也。又何有愿于人乎哉。此实良贵之在我而人不得如之何者也。回视人之膏粱文绣之不能自有而系乎人之予夺者。岂不万万哉。欲贵者人之同心也。而不思有求于此而营营屑屑于非所当求之地。亦独何心哉。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圣人之所以与人交际者。既不以享之多仪。而责人之所不可为者。亦不以责备为嫌。而不计人之所当为者也。何者。季子之于任。既为君居守。则邹异国也。为国居守者。其可越境见贤乎。特以币交者。礼意已备。而其越境。乃其势所不为也。孟子于此苟不有所斟酌。则此但知享之多仪。而不思夫人之所不可为者也。其可谓圣人时措之宜乎。储子者既为齐相。而平陆亦齐地也。虽异国其于往复。特不为耳。初不有犯境。有如季子之势不可为者也。而况国内之地乎。其所以币交而不往见者。其可谓及物之仪乎。虽圣之不责备者。岂不复计其所当为者而轻报于不当报之人乎。此所以币交则同。而其所以见不见则亦不得不尔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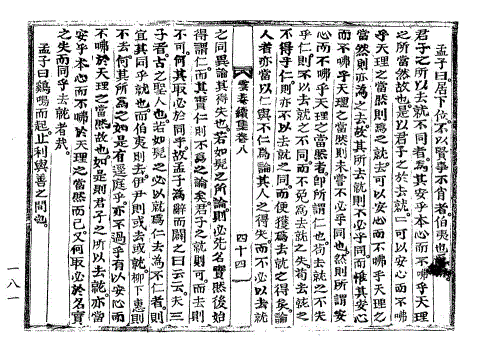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君子之所以去就不同者。为其安乎本心而不咈乎天理之所当然故也。是以君子之于去就。就可以安心而不咈乎天理之当然则为之就。去可以安心而不咈乎天理之当然则亦为之去。故其所去就则不必乎同。而惟其安心而不咈乎天理之当然则未尝不必乎同也。然则所谓安心而不咈乎天理之当然者。即所谓仁也。苟去就之不失乎仁。则不以去就之不同。而不免为去就之失。苟去就之不得乎仁。则亦不以去就之同。而便获为去就之得矣。论人者亦当以仁与不仁为论其人之得失。而不必以去就之同异论其得失也。若如髡之所论。则必先名实然后始得谓仁。而其实仁则不为之论矣。君子之就则可。而去则不可。何其取必于同乎。故孟子为辞而辟之曰云云。夫三子者。古之圣人也。若如髡之必以就为仁去为不仁者。则宜其同乎就也。而伯夷则去。伊尹则或去或就。柳下惠则不去。何其所为之如是有径庭乎。亦不过乎有以安心而不咈于天理之当然故也。如是则君子之所以去就。亦当安乎本心而不咈于天理之当然而已。又何取必于名实之失而同乎去就者哉。
孟子曰鸡鸣而起。止利与善之间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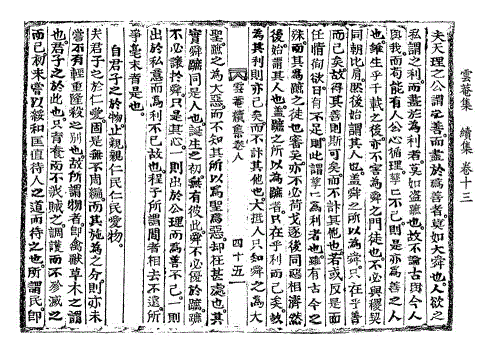 夫天理之公谓之善。而尽于为善者。莫如大舜也。人欲之私谓之利。而尽于为利者。莫如盗蹠也。故不论古与今人与我。而苟能有人公心循理。孳孳不已。则是亦为善之人也。虽生乎千载之后。亦不害为舜之门徒也。不必与稷契同朝比肩。然后始谓其人也。盖舜之所以为舜。只在乎善而已矣。故得其善则斯可矣。而不计其他也。若或反是而任情徇欲。日有不足。则此谓孳孳为利者也。虽有古今之殊。而其为蹠之徒也审矣。亦不必荷戈逐后同恶相济然后。始谓其人也。盖蹠之所以为蹠者。只在乎利而已矣。故为其利则亦已矣。而不计其他也。大抵人只知舜之为大圣。蹠之为大恶。而不知其所以为圣为恶。却在甚处也。其实舜蹠同是人也。诞生之初。无有彼此。舜不必优于蹠。蹠不必让于舜。只是其心。一则出于公理而为善不已。一则出于私意而为利不已故也。程子所谓间者相去不远。所争毫末者是也。
夫天理之公谓之善。而尽于为善者。莫如大舜也。人欲之私谓之利。而尽于为利者。莫如盗蹠也。故不论古与今人与我。而苟能有人公心循理。孳孳不已。则是亦为善之人也。虽生乎千载之后。亦不害为舜之门徒也。不必与稷契同朝比肩。然后始谓其人也。盖舜之所以为舜。只在乎善而已矣。故得其善则斯可矣。而不计其他也。若或反是而任情徇欲。日有不足。则此谓孳孳为利者也。虽有古今之殊。而其为蹠之徒也审矣。亦不必荷戈逐后同恶相济然后。始谓其人也。盖蹠之所以为蹠者。只在乎利而已矣。故为其利则亦已矣。而不计其他也。大抵人只知舜之为大圣。蹠之为大恶。而不知其所以为圣为恶。却在甚处也。其实舜蹠同是人也。诞生之初。无有彼此。舜不必优于蹠。蹠不必让于舜。只是其心。一则出于公理而为善不已。一则出于私意而为利不已故也。程子所谓间者相去不远。所争毫末者是也。自君子之于物。止亲亲仁民仁民爱物。
夫君子之于仁爱。固是无不周编。而其施为之分。则亦未尝不有轻重隆杀之别也。故所谓物者。即禽兽草木之谓也。君子之于此也。只育养而不戕贼之。调护而不殄灭之而已。初未尝以绥和匡直待人之道而待之也。所谓民。即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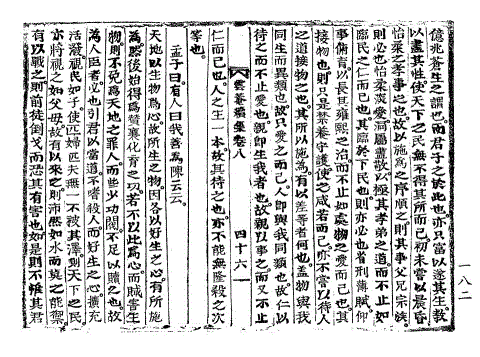 亿兆苍生之谓也。而君子之于此也。亦只富以遂其生。教以尽其性。使天下之民无不得其所而已。初未尝以晨昏怡柔之孝事之也。故以施为之序顺之。则其事父兄宗族。则必也怡柔深爱。洞属尽敬。以极其孝弟之道。而不止如临民之仁而已也。其临于下民也。则亦必也省刑薄赋。仰事俯育。以长其雍熙之治。而不止如处物之爱而已也。其接物也。则只是禁养守护。使之咸若而已。亦不尝以待人之道接物之也。其所以施为。有以差等者何也。盖物与我同生而异类也。故只爱之而已。人即与我同类也。故仁以待之而不止爱也。亲即生我者也。故亲以事之。而又不止仁而已也。人之生一本。故其待之也。亦不能无隆杀之次等也。
亿兆苍生之谓也。而君子之于此也。亦只富以遂其生。教以尽其性。使天下之民无不得其所而已。初未尝以晨昏怡柔之孝事之也。故以施为之序顺之。则其事父兄宗族。则必也怡柔深爱。洞属尽敬。以极其孝弟之道。而不止如临民之仁而已也。其临于下民也。则亦必也省刑薄赋。仰事俯育。以长其雍熙之治。而不止如处物之爱而已也。其接物也。则只是禁养守护。使之咸若而已。亦不尝以待人之道接物之也。其所以施为。有以差等者何也。盖物与我同生而异类也。故只爱之而已。人即与我同类也。故仁以待之而不止爱也。亲即生我者也。故亲以事之。而又不止仁而已也。人之生一本。故其待之也。亦不能无隆杀之次等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云云。
天地以生物为心。故所生之物。因各以好生之心。有所施为。然后始得为赞襄化育之功。若不以此为心。而贼害生物。则不免为天地之罪人。而些少功阀。不足以赎之也。故为人臣者。必也引君以当道。不嗜杀人。而好生之心。扩充活泼。视民如子。使匹妇匹夫无一不被其泽。则天下之民。亦将视之如父母。故有以来之。则沛然如水而莫之能御。有以战之。则前徒倒戈而恐其有害也。如是则不惟其君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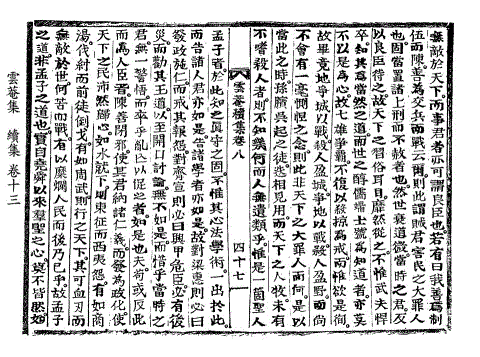 无敌于天下。而事君者亦可谓良臣也。若有曰我善为制伍而陈。善为交兵而战云尔。则此谓贼君害民之大罪人也。固当置诸上刑而不赦者也。然世衰道微。当时之君。反以良臣待之。故天下之习俗耳目。靡然从之。不惟武夫悍卒。知其为当然之道。而世之醇儒端士号为知道者。亦莫不以是为心。故七雄争霸。不复以杀掠为戒。而惟欲是徇。故毕竟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而尚不会有一毫恻怛之念。则此非天下之大罪人而何。是以当此之时。孙膑吴起之徒。迭相见用。而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则不知几何而人无遗类乎。惟是一个圣人孟子者。于此知之真守之固。不惟其心法学术。一出于此。而告诸人君亦如是。告诸学者亦如是。故对梁惠则必曰发政施仁。而戒其报怨。对齐宣则必曰兴甲危臣。必有后灾。而劝其王道。以至开口讨论。无不如是。而惜乎当时之君。无一警悟。而卒乎乱亡以促之者。如是也夫。苟或反此而为人臣者。陈善闭邪。使其君纳诸仁义。而发为政化。使天下之民沛然归心。如水就下。则东征而西夷怨。有如商汤。伐纣而前徒倒戈。有如周武。则行之天下。其可血刃而无敌于世。何苦而战。有以糜烂人民而后乃已乎。故孟子之道。非孟子之道也。实自尧舜以来群圣之心。莫不皆然。如
无敌于天下。而事君者亦可谓良臣也。若有曰我善为制伍而陈。善为交兵而战云尔。则此谓贼君害民之大罪人也。固当置诸上刑而不赦者也。然世衰道微。当时之君。反以良臣待之。故天下之习俗耳目。靡然从之。不惟武夫悍卒。知其为当然之道。而世之醇儒端士号为知道者。亦莫不以是为心。故七雄争霸。不复以杀掠为戒。而惟欲是徇。故毕竟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而尚不会有一毫恻怛之念。则此非天下之大罪人而何。是以当此之时。孙膑吴起之徒。迭相见用。而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则不知几何而人无遗类乎。惟是一个圣人孟子者。于此知之真守之固。不惟其心法学术。一出于此。而告诸人君亦如是。告诸学者亦如是。故对梁惠则必曰发政施仁。而戒其报怨。对齐宣则必曰兴甲危臣。必有后灾。而劝其王道。以至开口讨论。无不如是。而惜乎当时之君。无一警悟。而卒乎乱亡以促之者。如是也夫。苟或反此而为人臣者。陈善闭邪。使其君纳诸仁义。而发为政化。使天下之民沛然归心。如水就下。则东征而西夷怨。有如商汤。伐纣而前徒倒戈。有如周武。则行之天下。其可血刃而无敌于世。何苦而战。有以糜烂人民而后乃已乎。故孟子之道。非孟子之道也。实自尧舜以来群圣之心。莫不皆然。如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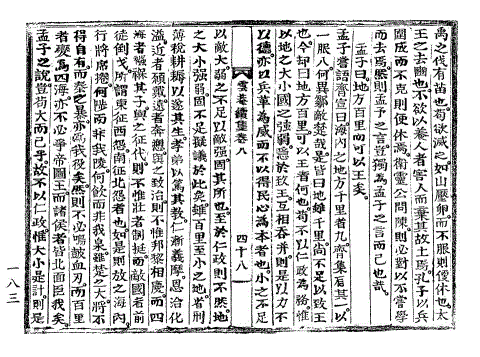 禹之伐有苗也。苟欲灭之。如山压卵。而不服则便休也。太王之去豳也。不欲以养人者害人而弃其故土焉。孔子以兵围成而不克则便休焉。卫灵公问陈。则必对以不尝学而去焉。然则孟子之言。岂独为孟子之言而已也哉。
禹之伐有苗也。苟欲灭之。如山压卵。而不服则便休也。太王之去豳也。不欲以养人者害人而弃其故土焉。孔子以兵围成而不克则便休焉。卫灵公问陈。则必对以不尝学而去焉。然则孟子之言。岂独为孟子之言而已也哉。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
孟子尝语齐宣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异邹敌楚哉。是皆曰地虽千里。尚不足以致王也。今却曰地方百里。可以王者何也。苟不以仁政为务。惟以地之大小国之强弱。急于致王。互相吞并。则是以力不以德。亦以兵革为威而不以得民心为本者也。小之不足以敌大。弱之不足以敌强。固其所也。至于仁政则不然。地之大小强弱。固不足拟议于此矣。虽百里至小之地。省刑薄税耕耨以遂其生。孝弟以笃其教。仁渐义摩。恩洽化溢。近者愿戴。远者奔愬。与之致治。则不惟邦黎相庆。而四海者襁褓其子。与之征代。则不惟壮者制挺。而敌国者前徒倒戈。所谓东征西怨。南征北怨者也。如是则放之海内。行将席捲。何陟而非我陵。何饮而非我泉。虽楚之大。将不得自有。而秦之暴。亦为我役矣。然则不必鸣鼓血刃。而百里者变为四海。亦不必争帝图王。而诸侯者皆北面臣我矣。孟子之说。岂苟大而已乎。故不以仁政。惟大小是计。则是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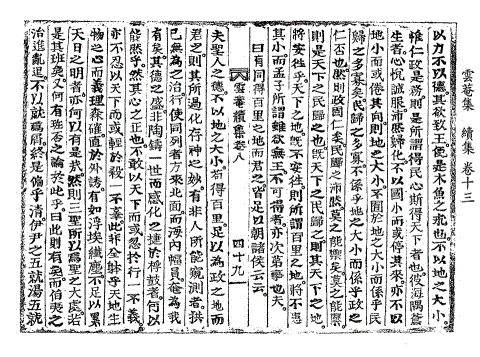 以力不以德。其欲致王。便是木鱼之求也。不以地之大小。惟仁政是务。则是所谓得民心斯得天下者也。彼海隅苍生者。心悦诚服。沛然归化。不以国小而或停其来。亦不以地小而或倦其向。则地之大小。不囿于地之大小而系乎民归之多寡矣。民归之多寡。不系乎地之大小而系乎政之仁否也。然则政固仁矣。民归之沛然。莫之能御矣。莫之能御。则是天下之民归之也。既天下之民归之。则其天下之地。将安往乎。天下之地。既不安往。则所谓百里之地。将不患其小。而孟子所谓虽欲无王。不可得者。亦次第事也夫。
以力不以德。其欲致王。便是木鱼之求也。不以地之大小。惟仁政是务。则是所谓得民心斯得天下者也。彼海隅苍生者。心悦诚服。沛然归化。不以国小而或停其来。亦不以地小而或倦其向。则地之大小。不囿于地之大小而系乎民归之多寡矣。民归之多寡。不系乎地之大小而系乎政之仁否也。然则政固仁矣。民归之沛然。莫之能御矣。莫之能御。则是天下之民归之也。既天下之民归之。则其天下之地。将安往乎。天下之地。既不安往。则所谓百里之地。将不患其小。而孟子所谓虽欲无王。不可得者。亦次第事也夫。曰有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云云。
夫圣人之德。不以地之大小。苟得百里。足以为政之地而君之。则其所过化存神之妙。有非人所能窥测者。拱己无为之治。行使同列者方来北面。而海内幅员。奄为我有矣。其德之盛。非陶铸一世而感化之捷于桴鼓者。何以能然乎。然其心之正也。不敢以天下而或忽于行一不义。亦不忍以天下而或轻于杀一不辜。此非全体乎天地生物之心而义理森确。直于外诱。有如浮埃纤尘。不足以累天日之明者。亦何以有是哉。然则三圣所以为圣之大处。若是其班矣。又何有班否之论于此乎。曰此则有矣。而伯夷之治进乱退。不以就为屑。终是偏乎清。伊尹之五就汤五就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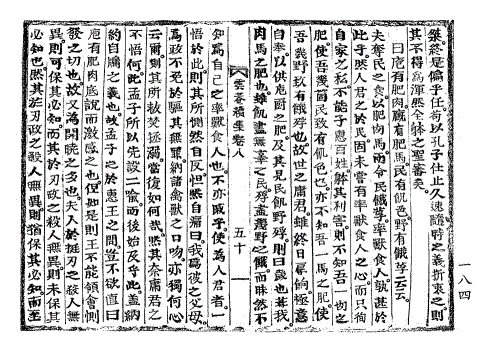 桀。终是偏乎任。苟以孔子仕止久速随时之义折衷之。则其不得为浑然全体之圣审矣。
桀。终是偏乎任。苟以孔子仕止久速随时之义折衷之。则其不得为浑然全体之圣审矣。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云云。
夫夺民之食。以肥肉马。而令民饿莩。率兽食人。孰甚于此乎。然人君之于民。固未尝有率兽食人之心。而只徇自家之私。不能子惠百姓。体其利害。则不知吾一肉之肥。使吾几个民致有饥色也。亦不知吾一马之肥。使吾几野致有饿殍也。故世之庸君。虽终日厚饷。极意自奉。以供庖厨之肥。及其见民饥野殍。则曰岁也非我。肉马之肥也。虽饥尽无辜之民。殍尽几野之饿。而昧然不知为自己之率兽食人也。不亦戚乎。使为人君者。一悟于此。则其所恻然自反。怛然自痛曰。我为彼之父母。为政不免于驱其无罪。纳诸禽兽之口吻。亦独何心云尔。则其所救焚拯溺。当复如何哉。然其奈庸君之不悟何。此孟子所以先设二喻。而后始及乎此。盖纳约自牖之义也。故孟子之于惠王之问。岂不欲直曰庖有肥肉底说而激感之也。但如是则王不能领会恻发之切也。故又为开晓之多也。夫人于挺刃之杀人无异。则可保其必知。而其于刃政之杀人无异。则未保其必知也。然其于刃政之杀人无异。则犹保其必知。而至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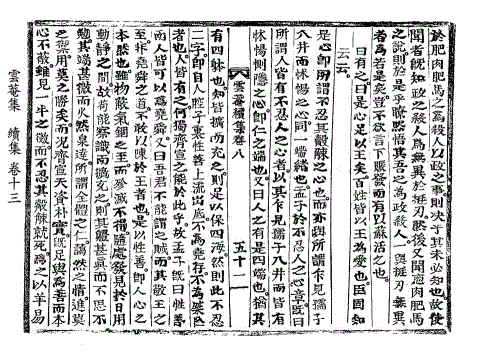 于肥肉肥马之为杀人以政之事。则决乎其未必知也。故使闻者既知政之杀人为无异于挺刃。然后又闻庖肉肥马之说。则于是乎瞭然悟其吾之为政杀人。一与挺刃无异者为若是矣。岂不欲言下赈发而有以苏活之也。
于肥肉肥马之为杀人以政之事。则决乎其未必知也。故使闻者既知政之杀人为无异于挺刃。然后又闻庖肉肥马之说。则于是乎瞭然悟其吾之为政杀人。一与挺刃无异者为若是矣。岂不欲言下赈发而有以苏活之也。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云云。
是心即所谓不忍其觳觫之心也。而亦与所谓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之心。同一端绪也。孟子于不忍人之心章。既曰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其乍见孺子入井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即仁之端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知皆扩而充之。则足以保四海。然则此不忍二字。即自人腔子里性善上流出底。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也。人皆有之。何独齐宣之能于此乎。故孟子既曰性善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吾君不能谓之贼。而其敬王之至。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者也。是以性善。即人心之本然也。虽物蔽气锢之至。而殄灭不得。随处发见于日用动静之间。故苟能察识而扩充之。则其体甚真而不思不勉。其端甚微而火然泉达。所谓全体之仁。蔼然之情。进莫之御。用莫之胜矣。而况齐宣天资朴实。既足与为善而本心不蔽。虽见一牛之微。而不忍其觳觫就死。为之以羊易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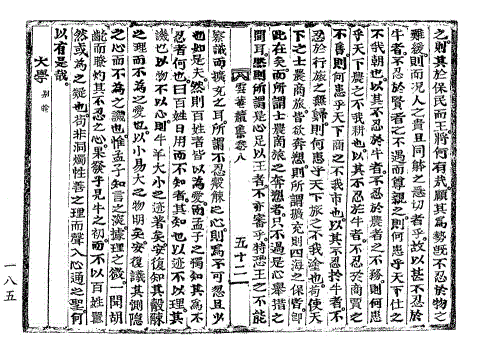 之。则其于保民而王。将何有哉。顾其为势既不忍于物之难缓。则而况人之贵且同体之急切者乎。故以甚不忍于牛者。不忍于贤者之不遇而尊亲之。则何患乎天下仕之不我朝也。以其不忍于牛者。不忍于农者之不务。则何患乎天下农之不我耕也。以其不忍于牛者。不忍于商贾之不售。则何患乎天下商之不我市也。以其不忍于牛者。不忍于行旅之无归。则何患乎天下旅之不我涂也。苟使天下之士农商旅。皆欲奔愬。则所谓扩充则四海之保者。即此在矣。而所谓士农商旅之奔愬者。只不过是心举措之间耳。然则所谓是心足以王者。不亦审乎。特恐王之不能察识而扩充之耳。所谓不忍觳觫之心。则为不可忽且少也如是夫。然则百姓者皆以为爱。而孟子之独知其为不忍者何也。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其知也以迹不以理。其讥也以物不以心。则牛羊大小之迹著矣。安复知其觳觫之理而不为之爱也。以小易大之物明矣。安复议其恻隐之心而不为之讥也。惟孟子知言之深。据理之微。一闻胡龁而瞭灼其不忍之心。果发乎见牛之初。而不以百姓嚣然或为之疑也。苟非洞烛性善之理而声入心通之圣。何以有是哉。
之。则其于保民而王。将何有哉。顾其为势既不忍于物之难缓。则而况人之贵且同体之急切者乎。故以甚不忍于牛者。不忍于贤者之不遇而尊亲之。则何患乎天下仕之不我朝也。以其不忍于牛者。不忍于农者之不务。则何患乎天下农之不我耕也。以其不忍于牛者。不忍于商贾之不售。则何患乎天下商之不我市也。以其不忍于牛者。不忍于行旅之无归。则何患乎天下旅之不我涂也。苟使天下之士农商旅。皆欲奔愬。则所谓扩充则四海之保者。即此在矣。而所谓士农商旅之奔愬者。只不过是心举措之间耳。然则所谓是心足以王者。不亦审乎。特恐王之不能察识而扩充之耳。所谓不忍觳觫之心。则为不可忽且少也如是夫。然则百姓者皆以为爱。而孟子之独知其为不忍者何也。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其知也以迹不以理。其讥也以物不以心。则牛羊大小之迹著矣。安复知其觳觫之理而不为之爱也。以小易大之物明矣。安复议其恻隐之心而不为之讥也。惟孟子知言之深。据理之微。一闻胡龁而瞭灼其不忍之心。果发乎见牛之初。而不以百姓嚣然或为之疑也。苟非洞烛性善之理而声入心通之圣。何以有是哉。大学(别拾)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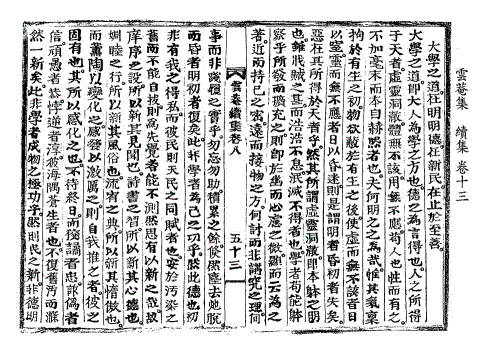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即大人为学之方也。德之为言得也。人之所得于天者。虚灵洞澈。体无不该。用无不应。苟人也性而有之。不加毫末而本自赫然者也。夫何明之之为哉。惟其气禀拘于有生之初。物欲蔽于有生之后。使虚而无不该者日以窒。灵而无不应者日以昏迷。则是谓明者昏初者失矣。恶在其所得于天者乎。然其所谓虚灵洞澈。即本体之明也。虽戕贼之甚。而浩浩不息。泯灭不得者也。学者苟能体察乎所发而扩充之。则即于幽而心虑之微。显而云为之著。近而持己之密。远而接物之方。何讨而非讲究之理。何事而非践履之实乎。勿忘勿助。积累之馀。倏然尘去灺脱。而昏者明初者复矣。此非学者为己之功乎。然此德也初非有我之得私。而彼民则天民之同赋者也。安于污染之旧而不能自拔。则为先觉者能不测然思有以新之哉。故庠序之设。所以新其见闻也。诗书之习。所以新其心德也。姻睦之行。所以新其风俗也。流宥之典。所以新其惰傲也。而薰陶以变化之。感发以激厉之。则自我推之者。彼之固有也。其所以感化之也。不待终日。而狡谲者忠。诈伪者信。顽愚者恭。悖逆者淳。彼海隅苍生者也。不复旧污而涤然一新矣。此非学者成物之极功乎。然则民之新。非德明
云庵续集卷之十三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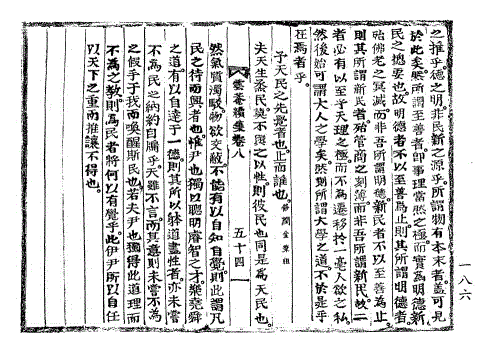 之推乎。德之明。非民新之源乎。所谓物有本末者。盖可见于此矣。然所谓至善者。即事理当然之极。而实为明德新民之总要也。故明德者不以至善为止。则其所谓明德者。殆佛老之冥灭。而非吾所谓明德。新民者不以至善为止。则其所谓新民者。殆管商之刻薄。而非吾所谓新民。故二者必有以至乎天理之极。而不为迁移于一毫人欲之私。然后始可谓大人之学矣。然则所谓大学之道。不于是乎在焉者乎。
之推乎。德之明。非民新之源乎。所谓物有本末者。盖可见于此矣。然所谓至善者。即事理当然之极。而实为明德新民之总要也。故明德者不以至善为止。则其所谓明德者。殆佛老之冥灭。而非吾所谓明德。新民者不以至善为止。则其所谓新民者。殆管商之刻薄。而非吾所谓新民。故二者必有以至乎天理之极。而不为迁移于一毫人欲之私。然后始可谓大人之学矣。然则所谓大学之道。不于是乎在焉者乎。予天民之先觉者也。止而谁也。(修润金秉祖)
夫天生烝民。莫不与之以性。则彼民也同是为天民也。然气质浊驳。物欲交蔽。不能有以自知自觉。则此谓凡民之待而兴者也。惟尹也独以聪明睿智之才。乐尧舜之道。有以自达于一德。则其所以体道尽性者。亦未尝不为民之纳约自牖乎。天虽不言。而其意则未尝不为之假手于我而唤醒斯民也。若夫尹也独得此道理而不为之教。则为民者将何以有觉乎。此伊尹所以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推让不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