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问目
问目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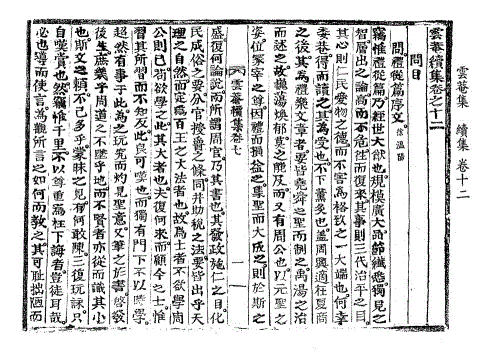 [杂著]
[杂著][答徐温阳熙淳(二十九条)]
问。礼从篇序文。(徐温阳)
窃惟礼从篇。乃经世大猷也。规模广大。品节纤悉。独见之智。层出之论。高而不危。往而复来。其事则三代治平之目。其心则仁民爱物之德。而不害为格致之一大端也。何幸委巷。得而读之。其为受也。不下薰炙也。盖周兴适在夏商之后。其为礼乐文章者。要皆尧舜之圣而制之。禹汤之治而述之。故巍荡焕郁。莫之能及。而又有周公也。以元圣之姿。位冢宰之尊。因礼而损益之。集圣而大成之。则于斯之盛。复何论说。而所谓周官。乃其书也。其发政施仁之目。化民成俗之要。分官授爵之条。同井助税之法。要皆出乎天理之自然。而定为百王之大法者也。故为士者不欲学周公则已。苟欲学之。此其大者也。夫复何求。而顾今之士。惟习其所习而不知反。此良可叹也。而独有门下不以时学。超然有事于此。为之玩究而灼见圣意。又笔之于书。启发后生。庶几乎周道之不坠乎地。而不贤者亦从而识其小也。斯文之赖。不已多乎。蒙昧之见。有何敢陈。三复玩咏。只自叹赏也。然窃惟千里。不以尊重为枉下诲者。岂徒耳哉。必也导而使言。为观所言之如何而教之。其可耻拙陋而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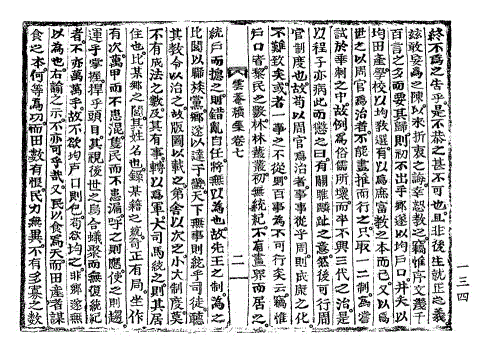 终不为之告乎。是不恭之甚不可也。且非后生就正之义。玆敢妄为之陈。以求折衷之诲。幸恕教之。窃惟序文几千百言之多而要其归。则初不出乎乡遂以均户口。井夫以均田产。学校以均教选。有以为庶富教之本而已。又以为世之以周官为治者。不能尽推而行之。只取一二制。为尝试于乖剌之中。故例为俗儒所坏。而卒不兴三代之治。是以程子亦病此而惩之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制度也。故苟以周官为治者。事事从乎周。则成康之化。不难致矣。或者一事之不从。则百事为不可行矣云。窃惟户口者。黎民之数。林林䕺丛。初无统纪。不有画界而居之。统户而总之。则错乱自任。将无以为也。故先王之制。为之比闾以联族党。乡遂以达于畿。天下无事则统乎司徒。听其教令以治之。故版图以载之。第舍以次之。小大制度。莫不有成法之数。及其有事。转以为军。大司马统之。则其居住也。比某乡之闾。其姓名也。录某籍之统。奇正有局。坐作有次。万甲而不患混。只民而不患漏。呼之则应。使之则趋。运乎掌握。捍乎头目。其视后世之乌合蚁聚而无复统纪者。不亦万万乎。故不欲均户口则已。苟欲均之。非乡遂无以为也。右谕之示。不亦可乎哉。又民以食为天。而田产者谋食之本。何等为功。而田数有恨。民力无异。不有多寡之数
终不为之告乎。是不恭之甚不可也。且非后生就正之义。玆敢妄为之陈。以求折衷之诲。幸恕教之。窃惟序文几千百言之多而要其归。则初不出乎乡遂以均户口。井夫以均田产。学校以均教选。有以为庶富教之本而已。又以为世之以周官为治者。不能尽推而行之。只取一二制。为尝试于乖剌之中。故例为俗儒所坏。而卒不兴三代之治。是以程子亦病此而惩之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制度也。故苟以周官为治者。事事从乎周。则成康之化。不难致矣。或者一事之不从。则百事为不可行矣云。窃惟户口者。黎民之数。林林䕺丛。初无统纪。不有画界而居之。统户而总之。则错乱自任。将无以为也。故先王之制。为之比闾以联族党。乡遂以达于畿。天下无事则统乎司徒。听其教令以治之。故版图以载之。第舍以次之。小大制度。莫不有成法之数。及其有事。转以为军。大司马统之。则其居住也。比某乡之闾。其姓名也。录某籍之统。奇正有局。坐作有次。万甲而不患混。只民而不患漏。呼之则应。使之则趋。运乎掌握。捍乎头目。其视后世之乌合蚁聚而无复统纪者。不亦万万乎。故不欲均户口则已。苟欲均之。非乡遂无以为也。右谕之示。不亦可乎哉。又民以食为天。而田产者谋食之本。何等为功。而田数有恨。民力无异。不有多寡之数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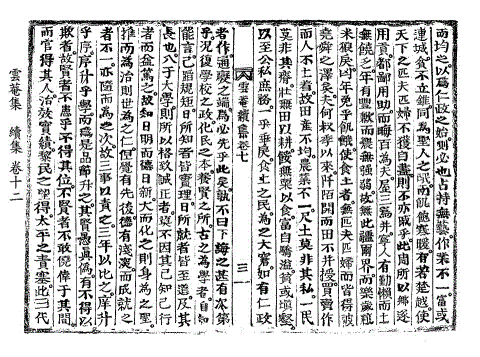 而均之。以为仁政之始。则必也占持无艺。作业不一。富或连城。贫不立锥。同为圣人之氓。而饥饱寒暖。有若楚越。使天下之匹夫匹妇不获自尽。则不亦戚乎。此周所以乡遂用贡。都鄙用助。而亩百为夫。屋三为井。宁人有勤懒而土无饶乏。年有丰歉而农无强弱。故无此疆尔界。而乐岁粒米狼戾。凶年免乎饥饿。使食土者。无匹夫匹妇而皆得被尧舜之泽矣。夫何叔季以来。阡陌开而田不井授。买卖作而人不土着。故田产不均。农业不一。尺土莫非其私。一民莫非其瘠。壮无田以耕。馁无粟以食。富自骄溢。贫或填壑。以至公私庶务。一乎乖戾。食土之民。为之大窘。如有仁政者作。通变之端。为必先乎此矣。孰不曰下诲之甚有次第乎。况复学校之政。化民之本。养贤之所。古之为学者。自知能言。已蹈规矩。日所知者皆实理。日所就者皆至道。及其长也。入于大学。则所以格致诚正者。莫不因其已知已行者而益笃之。故知日明而德日新。大而化之则身为之圣。推而为治则世为之仁。但觉有先后。德有浅深。而成就之者不一。亦随而为之次。故三事以责之。三年以比之。庠升乎序。序升乎学。而为是品节升之。其贤愚真伪。有不得以欺者。故贤者不患乎不得其位。不贤者不敢侥倖于其间。而官得其人。治效实绩。黎民之望得。太平之责塞。此三代
而均之。以为仁政之始。则必也占持无艺。作业不一。富或连城。贫不立锥。同为圣人之氓。而饥饱寒暖。有若楚越。使天下之匹夫匹妇不获自尽。则不亦戚乎。此周所以乡遂用贡。都鄙用助。而亩百为夫。屋三为井。宁人有勤懒而土无饶乏。年有丰歉而农无强弱。故无此疆尔界。而乐岁粒米狼戾。凶年免乎饥饿。使食土者。无匹夫匹妇而皆得被尧舜之泽矣。夫何叔季以来。阡陌开而田不井授。买卖作而人不土着。故田产不均。农业不一。尺土莫非其私。一民莫非其瘠。壮无田以耕。馁无粟以食。富自骄溢。贫或填壑。以至公私庶务。一乎乖戾。食土之民。为之大窘。如有仁政者作。通变之端。为必先乎此矣。孰不曰下诲之甚有次第乎。况复学校之政。化民之本。养贤之所。古之为学者。自知能言。已蹈规矩。日所知者皆实理。日所就者皆至道。及其长也。入于大学。则所以格致诚正者。莫不因其已知已行者而益笃之。故知日明而德日新。大而化之则身为之圣。推而为治则世为之仁。但觉有先后。德有浅深。而成就之者不一。亦随而为之次。故三事以责之。三年以比之。庠升乎序。序升乎学。而为是品节升之。其贤愚真伪。有不得以欺者。故贤者不患乎不得其位。不贤者不敢侥倖于其间。而官得其人。治效实绩。黎民之望得。太平之责塞。此三代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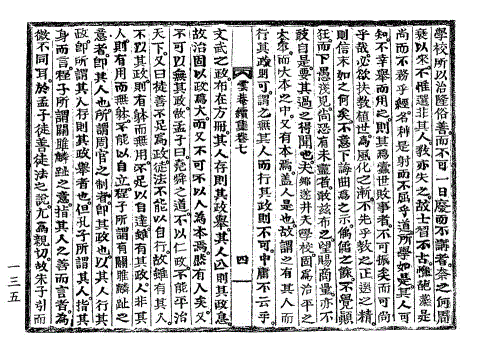 学校所以治隆俗善。而不可一日废而不讲者。奈之何周衰以来。不惟选非其人。教亦失之。故士习不古。惟葩藻是尚而不务乎经。名利是射而不屈乎道。所学如是。其人可知。不幸举而用之。则其为蠹世败事者。不可振矣而可尚乎哉。必欲扶教植世。为风化之渐。不先乎教之正选之精。则信末如之何矣。不意下诲曲为之示。偊偊之馀。不觉颠狂。而下愚浅见。尚恐有未尽者。敢玆布之。望赐商量。亦不敢自是。要其过之得闻也。夫乡遂井夫学校。固为治平之大本。而大本之中。又有本焉。盖人是也。故谓之有其人而行其政则可。谓之无其人而行其政则不可。中庸不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治固以政为大。而又不可不以人为本焉。然有人矣。又不可以无其政。故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虽有其人。不以其政。则有体而无用。不足以自达。虽有其政。人非其人。则有用而无体。不能以自立。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者。即其人也。所谓周官之制者。即其政也。以其人行其政。即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者也。但孔子所谓其人。指其身而言。程子所谓关雎麟趾之意。指其人之善而言者。为微不同耳。于孟子徒善徒法之说。尤为亲切。故朱子引而
学校所以治隆俗善。而不可一日废而不讲者。奈之何周衰以来。不惟选非其人。教亦失之。故士习不古。惟葩藻是尚而不务乎经。名利是射而不屈乎道。所学如是。其人可知。不幸举而用之。则其为蠹世败事者。不可振矣而可尚乎哉。必欲扶教植世。为风化之渐。不先乎教之正选之精。则信末如之何矣。不意下诲曲为之示。偊偊之馀。不觉颠狂。而下愚浅见。尚恐有未尽者。敢玆布之。望赐商量。亦不敢自是。要其过之得闻也。夫乡遂井夫学校。固为治平之大本。而大本之中。又有本焉。盖人是也。故谓之有其人而行其政则可。谓之无其人而行其政则不可。中庸不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治固以政为大。而又不可不以人为本焉。然有人矣。又不可以无其政。故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虽有其人。不以其政。则有体而无用。不足以自达。虽有其政。人非其人。则有用而无体。不能以自立。程子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者。即其人也。所谓周官之制者。即其政也。以其人行其政。即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者也。但孔子所谓其人。指其身而言。程子所谓关雎麟趾之意。指其人之善而言者。为微不同耳。于孟子徒善徒法之说。尤为亲切。故朱子引而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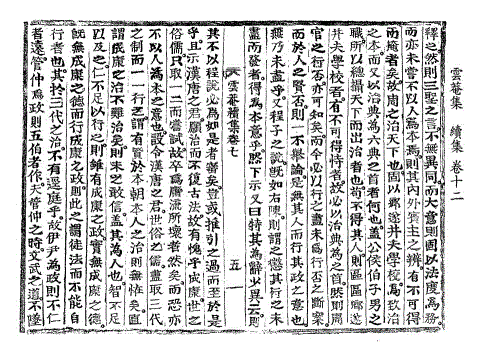 释之。然则三圣之言。不无异同。而大意则固以法度为务。而亦未尝不以人为本焉。则其内外宾主之辨。有不可得而掩者矣。故周之治天下也。固以乡遂井夫学校。为致治之本。而又以治典为六典之首者何也。盖公侯伯子男之职。所以总摄天下而出治者也。苟不得其人。则区区乡遂井夫学校者。有不可得恃者。故必以治典为之首。然则周官之行否。亦可知矣。而今必以行之尽未为行否之断案。而于人之贤否。则一不举论。是无其人而行其政之意也。无乃未尽乎。又程子之说。既如右陈。则谓之惩其行之未尽而发者。得为本意乎。然下示又曰特其为辞少异云。则其不以程说必为如是者审矣。岂或推引之过而至于是乎。且示汉唐之君。愿治而不复古法。故有愧乎成康。世之俗儒。只取一二而尝试。故卒为庸流所坏者然矣。而恐亦不以人为本之意也。设令汉唐之君。世俗之儒。尽取三代之制而一一行之。谓有贤于本朝本人之治则无怪矣。直谓成康之治不难治矣。则未之敢信。盖其为人也。智不足以及之。仁不足以行之。则虽有成康之政。实无成康之德。既无成康之德而行成康之政。则此之谓徒法而不能自行者也。其于三代之治。不有径庭乎。故伊尹为政则不仁者远。管仲为政则五伯者作。夫管仲之时。文武之道。不坠
释之。然则三圣之言。不无异同。而大意则固以法度为务。而亦未尝不以人为本焉。则其内外宾主之辨。有不可得而掩者矣。故周之治天下也。固以乡遂井夫学校。为致治之本。而又以治典为六典之首者何也。盖公侯伯子男之职。所以总摄天下而出治者也。苟不得其人。则区区乡遂井夫学校者。有不可得恃者。故必以治典为之首。然则周官之行否。亦可知矣。而今必以行之尽未为行否之断案。而于人之贤否。则一不举论。是无其人而行其政之意也。无乃未尽乎。又程子之说。既如右陈。则谓之惩其行之未尽而发者。得为本意乎。然下示又曰特其为辞少异云。则其不以程说必为如是者审矣。岂或推引之过而至于是乎。且示汉唐之君。愿治而不复古法。故有愧乎成康。世之俗儒。只取一二而尝试。故卒为庸流所坏者然矣。而恐亦不以人为本之意也。设令汉唐之君。世俗之儒。尽取三代之制而一一行之。谓有贤于本朝本人之治则无怪矣。直谓成康之治不难治矣。则未之敢信。盖其为人也。智不足以及之。仁不足以行之。则虽有成康之政。实无成康之德。既无成康之德而行成康之政。则此之谓徒法而不能自行者也。其于三代之治。不有径庭乎。故伊尹为政则不仁者远。管仲为政则五伯者作。夫管仲之时。文武之道。不坠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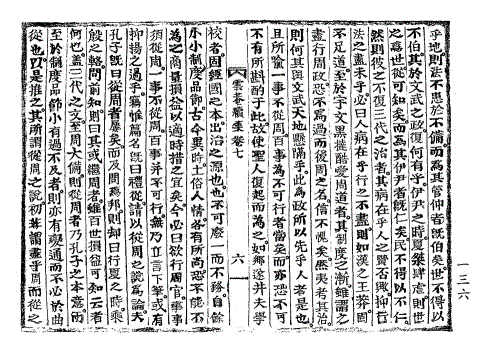 乎地。则法不患于不备。而为其管仲者既伯矣。世不得以不伯。其于文武之政。复何有乎。伊尹之时。夏桀肆虐。则世之为世。从可知矣。而为其伊尹者既仁矣。民不得以不仁。然则彼之不复三代之治者。其病在乎人之贤否欤。抑行法之尽未乎。必曰人病在乎行之不尽。则如汉之王莽。固不足道。至于宇文黑挞酷爱周道者。其制度之渐。虽谓之尽行周政。恐不为过而后周之名。信不愧矣。然夷考其治。则何其与文武天地悬隔乎。此为政所以先乎人者是也。且所喻一事不从周。百事为不可行者当矣。而亦恐不可不有所斟酌于此。故使圣人复起而为之。如乡遂井夫学校者。固经国之本。出治之源也。也不可废一而不务。自馀小小制度品节。古今异时。土俗人情。各有所尚。恐不能不为之商量损益以适时措之宜矣。今必曰欲行周官。事事须从周。一事不从周。百事并不可行。无乃立言下笔。或有抑扬之过乎。窃惟篇名既曰礼从。请以从周之说为论。夫孔子既曰从周者屡矣。而及问为邦。则却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问前知。则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损益可知云者何也。盖三代之文。至周大备。则从周者乃孔子之本意。而至于制度品节小有过不及者。则亦有变通而不必于曲从也。以是推之。其所谓从周之说。初非谓尽乎周而从之
乎地。则法不患于不备。而为其管仲者既伯矣。世不得以不伯。其于文武之政。复何有乎。伊尹之时。夏桀肆虐。则世之为世。从可知矣。而为其伊尹者既仁矣。民不得以不仁。然则彼之不复三代之治者。其病在乎人之贤否欤。抑行法之尽未乎。必曰人病在乎行之不尽。则如汉之王莽。固不足道。至于宇文黑挞酷爱周道者。其制度之渐。虽谓之尽行周政。恐不为过而后周之名。信不愧矣。然夷考其治。则何其与文武天地悬隔乎。此为政所以先乎人者是也。且所喻一事不从周。百事为不可行者当矣。而亦恐不可不有所斟酌于此。故使圣人复起而为之。如乡遂井夫学校者。固经国之本。出治之源也。也不可废一而不务。自馀小小制度品节。古今异时。土俗人情。各有所尚。恐不能不为之商量损益以适时措之宜矣。今必曰欲行周官。事事须从周。一事不从周。百事并不可行。无乃立言下笔。或有抑扬之过乎。窃惟篇名既曰礼从。请以从周之说为论。夫孔子既曰从周者屡矣。而及问为邦。则却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问前知。则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损益可知云者何也。盖三代之文。至周大备。则从周者乃孔子之本意。而至于制度品节小有过不及者。则亦有变通而不必于曲从也。以是推之。其所谓从周之说。初非谓尽乎周而从之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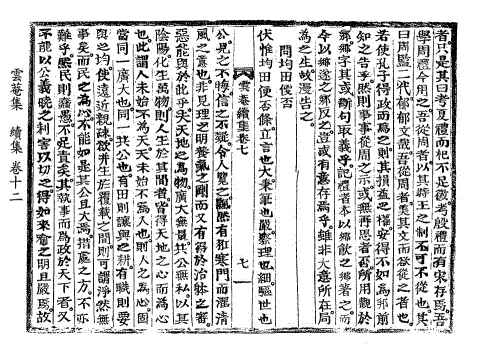 者。只是其曰考夏礼而杞不足徵。考殷礼而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者。以其时王之制不可不从也。其曰周监二代。郁郁文哉。吾从周者。美其文而欲从之者也。若使孔子得政而为之。则其损益之权。安得不如为邦前知之告乎。然则事事从周之示。或无再思者否。所用观于乡。乡字其或断句取义乎。记礼者本以乡饮之乡著之。而今以乡遂之乡反之。岂或有意存焉乎。虽非大意所在。局为之生。故漫告之。
者。只是其曰考夏礼而杞不足徵。考殷礼而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者。以其时王之制不可不从也。其曰周监二代。郁郁文哉。吾从周者。美其文而欲从之者也。若使孔子得政而为之。则其损益之权。安得不如为邦前知之告乎。然则事事从周之示。或无再思者否。所用观于乡。乡字其或断句取义乎。记礼者本以乡饮之乡著之。而今以乡遂之乡反之。岂或有意存焉乎。虽非大意所在。局为之生。故漫告之。问均田便否
伏惟均田便否条。立言也大。秉笔也严。察理也细。驱世也公。见之不晦。信之不疑。令人览之。飘然有羾寒门而濯清风之意也。非见理之明养气之刚而又有得于治体之审。恶能与于此乎。夫天地之为物。广大无量。共公无私。以其阴阳。化生万物。则人生于其间者。皆得天地之心而为心也。此谓人未始不为天。天未始不为人也。则人之为心。固当同一广大也。同一共公也。有田则让与之耕。有职则要与之均。使远近亲疏。欲并生于覆载之间。则可谓净然无事矣。而民之为心。不能如是其公且大焉。措处之方。不亦难乎。然民则蠢愚。不足责矣。其执事而为政于天下者。又不能以公义晓之利害以切之。得如来喻之明且严焉。故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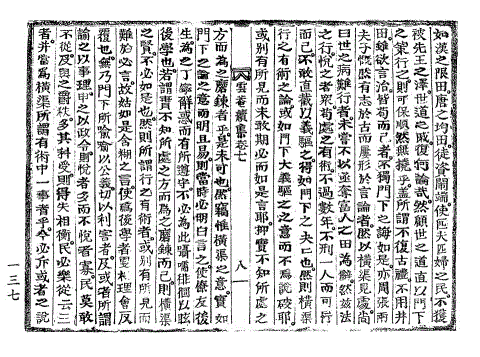 如汉之限田。唐之均田。徒资闹端。使匹夫匹妇之民。不获被先王之泽。世道之戚。复何论哉。然顾世之道直以门下之策行之。则可保顺然无挠乎。盖所谓不复古礼。不用井田。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者。不独门下之诲如是。亦周张两夫子慨然有志于古而屡形于言论者。然以横渠见处。尚曰世之病难行者。未尝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玆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不过数年。不刑一人而可行而已。不敢直截以义驱之。得如门下之夬夬也。然则横渠行之有术之论。或如门下大义驱之之意而不为说破耶。或别有所见而未敢期必而如是言耶。抑实不知所处之方而为之磨鍊者乎。是未可也。然窃惟横渠之意。实如门下之论之意而明且易。则当时必明白言之。使僚友后生。为之丁宁解惑而有所遵守。不必为此嗫嚅徘徊以眩后学也。若谓实不知所处之方而为之磨鍊而已。则横渠之贤。不必如是也。然则所谓行之有术者。或别有所见而难于必言。故姑如是含糊之言。使为后学者更相理会反覆也。无乃门下所喻喻以公义。切以利害者。及或者所谓谕之以事理。申之以政令。则悦者多而不悦者寡。民莫敢不从。及与之爵秩。多其科受。则得失相衡。民必乐从云三者。并当为横渠所谓有术中一事者乎。今必斥或者之说
如汉之限田。唐之均田。徒资闹端。使匹夫匹妇之民。不获被先王之泽。世道之戚。复何论哉。然顾世之道直以门下之策行之。则可保顺然无挠乎。盖所谓不复古礼。不用井田。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者。不独门下之诲如是。亦周张两夫子慨然有志于古而屡形于言论者。然以横渠见处。尚曰世之病难行者。未尝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玆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不过数年。不刑一人而可行而已。不敢直截以义驱之。得如门下之夬夬也。然则横渠行之有术之论。或如门下大义驱之之意而不为说破耶。或别有所见而未敢期必而如是言耶。抑实不知所处之方而为之磨鍊者乎。是未可也。然窃惟横渠之意。实如门下之论之意而明且易。则当时必明白言之。使僚友后生。为之丁宁解惑而有所遵守。不必为此嗫嚅徘徊以眩后学也。若谓实不知所处之方而为之磨鍊而已。则横渠之贤。不必如是也。然则所谓行之有术者。或别有所见而难于必言。故姑如是含糊之言。使为后学者更相理会反覆也。无乃门下所喻喻以公义。切以利害者。及或者所谓谕之以事理。申之以政令。则悦者多而不悦者寡。民莫敢不从。及与之爵秩。多其科受。则得失相衡。民必乐从云三者。并当为横渠所谓有术中一事者乎。今必斥或者之说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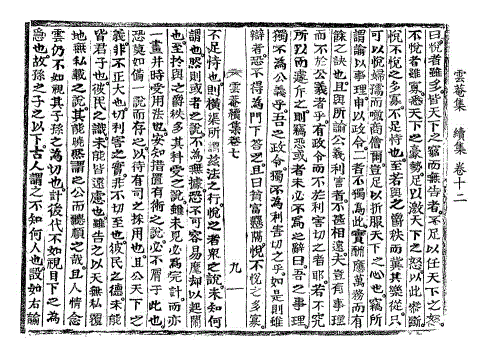 曰。悦者虽多。皆天下之穷而无告者。不足以任天下之怒。不悦者虽寡。悉天下之豪势。足以激天下之怒。以此参断。悦不悦之多寡。不足恃也。至若与之爵秩而冀其乐从。只可以悦妇孺而啖商侩尔。岂足以折服天下之心也。窃所谓谕以事理。申以政令。二者不独为此。实酬应万务而有馀之诀也。且与所谕公义利害者。不甚相远。夫岂有事理而不于公义者乎。有政令而不于利害切之者耶。若不究所以而遽斥之。则窃恐或者未必不为之辞曰。吾之事理。独不为公义乎。吾之政令。独不为利害切之乎。如是则虽辩者。恐不得为门下答之。且曰贫富悬隔。悦不悦之多寡。不足恃也。则横渠所谓玆法之行。悦之者众之说。未知何谓也。然则或者之说。不为无据。恐不可容易麾却以起闹也。至于与之爵秩多其科受之说。虽未见必为完计。而亦一画井时受用法也。安知措置有术之说。必不屑于此也。恐莫如备一说而存之。以待有司之采用也。且公天下之义。非不正大也。切利害之实。非不切至也。彼民之德。未能皆君子也。彼民之识。未能皆远虑也。虽告之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之说。其能晓然谓之公而听顺之哉。且人情念云仍不如视其子孙之为切也。计后代不如视目下之为急也。故孙之子之以下。古人谓之不知何人也。设如右谕
曰。悦者虽多。皆天下之穷而无告者。不足以任天下之怒。不悦者虽寡。悉天下之豪势。足以激天下之怒。以此参断。悦不悦之多寡。不足恃也。至若与之爵秩而冀其乐从。只可以悦妇孺而啖商侩尔。岂足以折服天下之心也。窃所谓谕以事理。申以政令。二者不独为此。实酬应万务而有馀之诀也。且与所谕公义利害者。不甚相远。夫岂有事理而不于公义者乎。有政令而不于利害切之者耶。若不究所以而遽斥之。则窃恐或者未必不为之辞曰。吾之事理。独不为公义乎。吾之政令。独不为利害切之乎。如是则虽辩者。恐不得为门下答之。且曰贫富悬隔。悦不悦之多寡。不足恃也。则横渠所谓玆法之行。悦之者众之说。未知何谓也。然则或者之说。不为无据。恐不可容易麾却以起闹也。至于与之爵秩多其科受之说。虽未见必为完计。而亦一画井时受用法也。安知措置有术之说。必不屑于此也。恐莫如备一说而存之。以待有司之采用也。且公天下之义。非不正大也。切利害之实。非不切至也。彼民之德。未能皆君子也。彼民之识。未能皆远虑也。虽告之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之说。其能晓然谓之公而听顺之哉。且人情念云仍不如视其子孙之为切也。计后代不如视目下之为急也。故孙之子之以下。古人谓之不知何人也。设如右谕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8L 页
 而得蒙后代之利。其肯为不知何人而散其一生之积乎。而况十世百世以后之苍苍者乎。而况素以衣锦食稻者之一朝为之蔬缊不亦难乎。而况子孙之得蒙厚利其可必乎。而况吾子孙其能如是之多且远乎。此皆愚民之所商量而不肯然处也。然则公天下之义。切利害之谕。恐未信其为民之必从也。夫量田比之画井。极易事也。一州比之天下。亦黑子也。然朱子尝为潭州也。请量于朝。朝廷沮之。议量于州。州人怒之。卒不遂意。为之大痛。若以井田之说。发于当时。则祸将不测矣。又非特一州之小而已乎。宋秦桧之秉威权也。得一量之则有之矣。而其时封植之木。人必书之曰李春年之墓而辱之。盖桧之所命而执事者也。夫量一州之田而尚如是。则于天下之为井也。从可知矣。然则不有圣后贤佐而为与之同德合力。则天下之事未可容易论也。故愚意窃以为不欲画井则已。必欲画之。必也君相相得。然后又得贤能而布罗天下。出治敷化。使天下之民。沛然归心于是也。徐以门下所谕公义利害之说。为之晓告以同其心。复以爵秩科受之事。补其不及。则恐不悖乎横渠所谓有术之行。而于画井也。亦多有得焉。未知如何。文一平居恒曰但患无其人。苟有其人而为政于天下。彼富人者自当献其田。有何可挠之端乎。及看朱
而得蒙后代之利。其肯为不知何人而散其一生之积乎。而况十世百世以后之苍苍者乎。而况素以衣锦食稻者之一朝为之蔬缊不亦难乎。而况子孙之得蒙厚利其可必乎。而况吾子孙其能如是之多且远乎。此皆愚民之所商量而不肯然处也。然则公天下之义。切利害之谕。恐未信其为民之必从也。夫量田比之画井。极易事也。一州比之天下。亦黑子也。然朱子尝为潭州也。请量于朝。朝廷沮之。议量于州。州人怒之。卒不遂意。为之大痛。若以井田之说。发于当时。则祸将不测矣。又非特一州之小而已乎。宋秦桧之秉威权也。得一量之则有之矣。而其时封植之木。人必书之曰李春年之墓而辱之。盖桧之所命而执事者也。夫量一州之田而尚如是。则于天下之为井也。从可知矣。然则不有圣后贤佐而为与之同德合力。则天下之事未可容易论也。故愚意窃以为不欲画井则已。必欲画之。必也君相相得。然后又得贤能而布罗天下。出治敷化。使天下之民。沛然归心于是也。徐以门下所谕公义利害之说。为之晓告以同其心。复以爵秩科受之事。补其不及。则恐不悖乎横渠所谓有术之行。而于画井也。亦多有得焉。未知如何。文一平居恒曰但患无其人。苟有其人而为政于天下。彼富人者自当献其田。有何可挠之端乎。及看朱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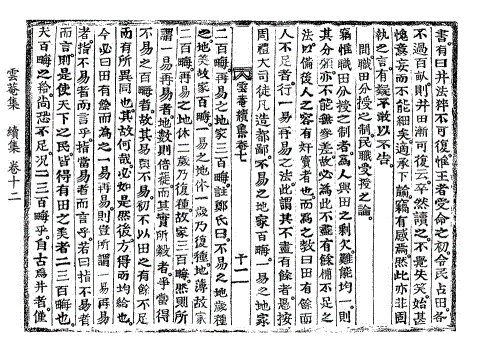 书。有曰井法猝不可复。惟王者受命之初。令民占田。各不过百亩。则井田渐可复云。卒然读之。不觉失笑。始甚愧意妄而不能细矣。适承下谕。窃有感焉。然此亦非固执之言。有疑不敢以不告。
书。有曰井法猝不可复。惟王者受命之初。令民占田。各不过百亩。则井田渐可复云。卒然读之。不觉失笑。始甚愧意妄而不能细矣。适承下谕。窃有感焉。然此亦非固执之言。有疑不敢以不告。问。职田分授之制。民职受授之论。
窃惟职田分授之制者。为人与田之剩欠。难能均一。则其分颁。亦不能无参差。故必为此不尽有馀补不足之法。以备后人之容有奸窦者也。而为之教曰田有馀而人不足者。行一易再易之法。此谓其不尽有馀者。愚按周礼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注郑氏曰。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然则所谓一易再易者。地数则倍蓰。而其实所谷者。争当得不易之百亩者。故其易与不易。初不以田之有馀不足而有所异同也。其故何哉。必如是然后。方得而均给也。今必曰田有馀而为之一易再易。则岂所谓一易再易者。指不易者而言乎。指当易者而言乎。若曰指不易者而言。则是使天下之民。皆得有田之美者二三百亩也。夫百亩之给。尚恐不足。况二三百亩乎。自古为井者。仅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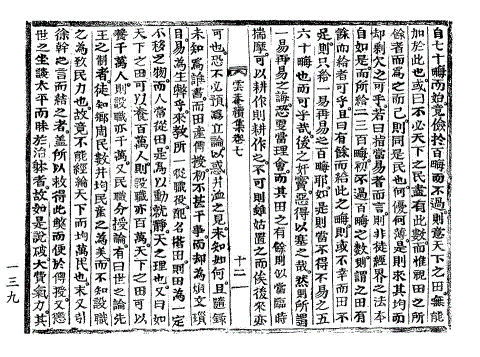 自七十亩而始。竟俭于百亩而不过。则意天下之田。无能加于此也。或曰不必天下之民尽有此数。而惟视田之所馀者而为之而已。则同是民也。何优何薄。是则求其均而却剩欠之可乎。若曰指当易者而言。则非徒经界之法本自如是。而所给二三百亩。初不过百亩之数。则谓之田有馀而给者可乎。且曰有馀而给此之亩。则或不幸而田不足。则只给一易再易之百亩耶。如是则当不得不易之五六十亩也而可乎哉。后之奸窦。恶得以塞之哉。然则所谓一易再易之诲。恐更当理会。而其田之有馀则似当临时揣摩。可以耕作则耕作之。不可则虽姑置之而俟后来亦可也。恐不必预为立论。以惑井洫之见。未知如何。且随录未知为谁书。而田产传授。初不甚干事。而却为烦文琐目。易为生弊乎。来教所一从职役。配名搭田。则田为一定不移之物。而人常从田。是为以动就静。天之理也。又曰如天下之田可以养百万人。则设职亦百万。天下之田可以养千万人。则设职亦千万。又民职分授论。有曰世之论先王之制者。徒知乡周民数井均民产之为美。而不知设职之为致民力也。故竟不能经纶天下而均万民也。末又引徐干之言而结之者。盖所以救得此弊而便于传授。又惩世之坐谈太平而昧于治体者。故如是说破。大费气力。其
自七十亩而始。竟俭于百亩而不过。则意天下之田。无能加于此也。或曰不必天下之民尽有此数。而惟视田之所馀者而为之而已。则同是民也。何优何薄。是则求其均而却剩欠之可乎。若曰指当易者而言。则非徒经界之法本自如是。而所给二三百亩。初不过百亩之数。则谓之田有馀而给者可乎。且曰有馀而给此之亩。则或不幸而田不足。则只给一易再易之百亩耶。如是则当不得不易之五六十亩也而可乎哉。后之奸窦。恶得以塞之哉。然则所谓一易再易之诲。恐更当理会。而其田之有馀则似当临时揣摩。可以耕作则耕作之。不可则虽姑置之而俟后来亦可也。恐不必预为立论。以惑井洫之见。未知如何。且随录未知为谁书。而田产传授。初不甚干事。而却为烦文琐目。易为生弊乎。来教所一从职役。配名搭田。则田为一定不移之物。而人常从田。是为以动就静。天之理也。又曰如天下之田可以养百万人。则设职亦百万。天下之田可以养千万人。则设职亦千万。又民职分授论。有曰世之论先王之制者。徒知乡周民数井均民产之为美。而不知设职之为致民力也。故竟不能经纶天下而均万民也。末又引徐干之言而结之者。盖所以救得此弊而便于传授。又惩世之坐谈太平而昧于治体者。故如是说破。大费气力。其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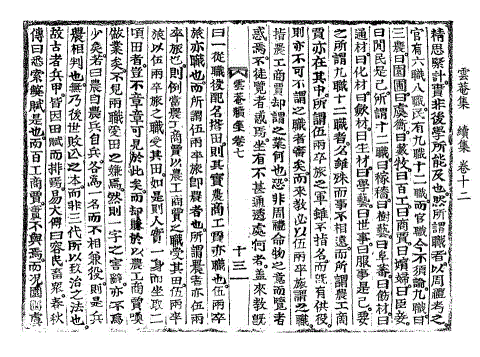 精思紧计。实非后学所能及也。然所谓职者。以周礼考之。官有六职八职。民有九职十二职。而官职今不须论。九职。曰三农。曰园圃。曰虞衡。曰薮牧。曰百工。曰商贾。曰嫔妇。曰臣妾。曰閒民是已。所谓十二职。曰稼穑。曰树艺。曰阜蕃。曰饬材。曰通材。曰化材。曰敛材。曰生材。曰学艺。曰世事。曰服事是已。要之所谓九职十二职者。名虽殊而事不相远。而所谓农工商贾亦在其中。所谓伍两卒旅之军虽不指名。而既有供役。则亦不可不谓之职者审矣。而来教必以伍两卒旅谓之职。指农工商贾却谓之业何也。恐非周礼命物之意而览者惑焉。不徒览者惑焉。坐有不甚通透处何者。盖来教既曰一从职役配名搭田。则其实农商工贾亦职也。伍两卒旅亦职也。而所谓伍两卒旅即农者也。所谓农者亦伍两卒旅也。则例当农工商贾以农工商贾之职受其田。伍两卒旅以伍两卒旅之职受其田。如是则人实一身而坐取二顷田者。岂不章章可见于此矣。而却赚于以农工商贾唤做业矣。不见两职受田之嫌焉。然则一字之害辞。亦不为少矣。若曰农自农兵自兵。各为一名而不相兼役。则是兵农相判也。无乃后世败亡之本。而非三代所以致治之法也。故古者兵甲。皆因田赋而排焉。易大传曰容民畜众。春秋传曰悉索弊赋是也。而百工商贾。实不与焉。而况园圃虞
精思紧计。实非后学所能及也。然所谓职者。以周礼考之。官有六职八职。民有九职十二职。而官职今不须论。九职。曰三农。曰园圃。曰虞衡。曰薮牧。曰百工。曰商贾。曰嫔妇。曰臣妾。曰閒民是已。所谓十二职。曰稼穑。曰树艺。曰阜蕃。曰饬材。曰通材。曰化材。曰敛材。曰生材。曰学艺。曰世事。曰服事是已。要之所谓九职十二职者。名虽殊而事不相远。而所谓农工商贾亦在其中。所谓伍两卒旅之军虽不指名。而既有供役。则亦不可不谓之职者审矣。而来教必以伍两卒旅谓之职。指农工商贾却谓之业何也。恐非周礼命物之意而览者惑焉。不徒览者惑焉。坐有不甚通透处何者。盖来教既曰一从职役配名搭田。则其实农商工贾亦职也。伍两卒旅亦职也。而所谓伍两卒旅即农者也。所谓农者亦伍两卒旅也。则例当农工商贾以农工商贾之职受其田。伍两卒旅以伍两卒旅之职受其田。如是则人实一身而坐取二顷田者。岂不章章可见于此矣。而却赚于以农工商贾唤做业矣。不见两职受田之嫌焉。然则一字之害辞。亦不为少矣。若曰农自农兵自兵。各为一名而不相兼役。则是兵农相判也。无乃后世败亡之本。而非三代所以致治之法也。故古者兵甲。皆因田赋而排焉。易大传曰容民畜众。春秋传曰悉索弊赋是也。而百工商贾。实不与焉。而况园圃虞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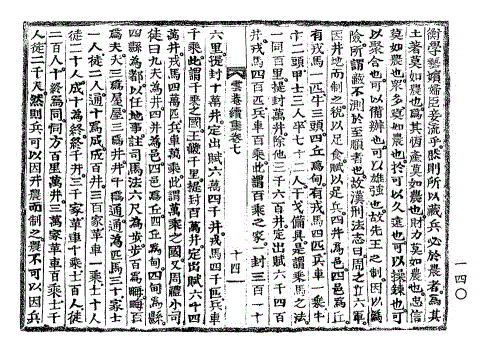 衡学艺嫔妇臣妾流乎。然则所以藏兵必于农者。为其土著莫如农也。为其恒产莫如农也。财力莫如农也。忠信莫如农也。众多莫如农也。于可以久远也。可以操鍊也。可以聚合也。可以备办也。可以雄强也。故先王之制。因以为险。所谓藏不测于至顺者也。故汉刑法志曰。周之立六军。因井地而制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他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谓千乘之国。王畿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此谓万乘之国。又周礼小司徒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注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然则兵可以因井农而制之。农不可以因兵
衡学艺嫔妇臣妾流乎。然则所以藏兵必于农者。为其土著莫如农也。为其恒产莫如农也。财力莫如农也。忠信莫如农也。众多莫如农也。于可以久远也。可以操鍊也。可以聚合也。可以备办也。可以雄强也。故先王之制。因以为险。所谓藏不测于至顺者也。故汉刑法志曰。周之立六军。因井地而制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他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谓千乘之国。王畿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此谓万乘之国。又周礼小司徒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注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然则兵可以因井农而制之。农不可以因兵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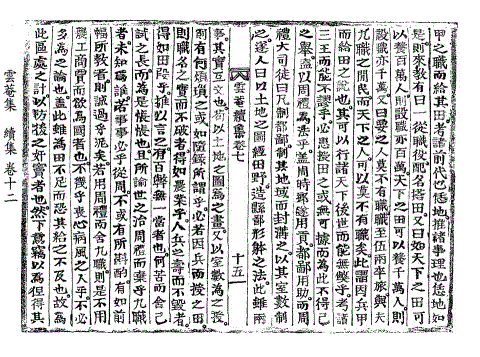 甲之职而给其田。考诸前代也恁地。推诸事理也恁地如是。则来教有曰一从职役。配名搭田。又曰如天下之田可以养百万人。则设职亦百万。天下之田可以养千万人。则设职亦千万。又曰要之人莫不有职。职至伍两卒旅。与夫九职之閒民。而天下之人。可以莫不有职矣。此谓因兵甲而给田之说也。其可以行诸天下后世而能无弊乎。考诸三王而能不谬乎。必患授田之或无可据而为此不得已之举。盍以周礼为法乎。盖周时乡遂用贡。都鄙用助。而周礼大司徒曰凡制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遂人曰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此虽两事。其实互文也。苟以土地之图为之画。又以室数为之授。则有何烦琐之或如随录所谓乎。必若因兵而授之田。则职名之实而不破者。得如农业乎。人兵之寿而不毁者。得如田段乎。推以言之。有百弊无一当者也。何苦而舍已试之长。而为是怅怅也。且所谕世之治周礼而弃乎九职者。未知为谁。若事事必乎从周。不或有所斟酌。有如前幅所教者。则诚过乎泥矣。若用周礼而舍九职。则是不用农工商贾而欲为国者也。不几乎丧心病风之人乎。不必多为之论也。盖此虽为田不足而恐其给之不及也。故为此区处之计。以防后之奸窦者也。然下意窃以为但得其
甲之职而给其田。考诸前代也恁地。推诸事理也恁地如是。则来教有曰一从职役。配名搭田。又曰如天下之田可以养百万人。则设职亦百万。天下之田可以养千万人。则设职亦千万。又曰要之人莫不有职。职至伍两卒旅。与夫九职之閒民。而天下之人。可以莫不有职矣。此谓因兵甲而给田之说也。其可以行诸天下后世而能无弊乎。考诸三王而能不谬乎。必患授田之或无可据而为此不得已之举。盍以周礼为法乎。盖周时乡遂用贡。都鄙用助。而周礼大司徒曰凡制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遂人曰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此虽两事。其实互文也。苟以土地之图为之画。又以室数为之授。则有何烦琐之或如随录所谓乎。必若因兵而授之田。则职名之实而不破者。得如农业乎。人兵之寿而不毁者。得如田段乎。推以言之。有百弊无一当者也。何苦而舍已试之长。而为是怅怅也。且所谕世之治周礼而弃乎九职者。未知为谁。若事事必乎从周。不或有所斟酌。有如前幅所教者。则诚过乎泥矣。若用周礼而舍九职。则是不用农工商贾而欲为国者也。不几乎丧心病风之人乎。不必多为之论也。盖此虽为田不足而恐其给之不及也。故为此区处之计。以防后之奸窦者也。然下意窃以为但得其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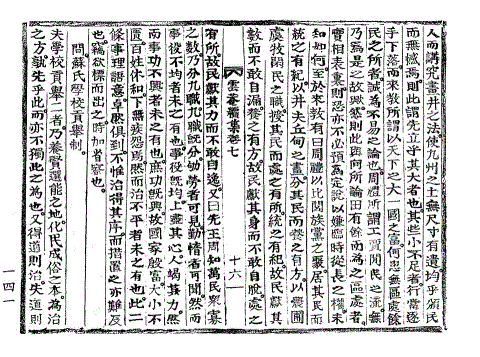 人而讲究画井之法。使九州之土无尺寸有遗。均乎颁民而无憾焉。则此谓先立乎其大者也。其些小不足者。行当逐手下落。而来教所谓以天下之大一国之富。何患无区处馀民之所者。诚为不易之论也。周礼所谓工贾閒民之流。无乃为是之故欤。然则此与向所论田有馀而为之区处者。实相表里。则恐亦不必预为定说以嫌临时从长之权。未知如何。至于来教有曰周礼以比闾族党之聚。居其民而统之有纪。以井夫丘甸之画。分其民而养之有方。以农圃虞牧闲民之职。授其民而处之有所。统之有纪。故民献其数而不敢自漏。养之有方。故民献其身而不敢自脱。处之有所。故民献其力而不敢自逸。又曰先王周知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九职既分。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上尽其心。人竭其力。然而事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疾怨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此二条事理语意。卓然俱到。不惟治得其序。而措置之亦难及也。窃欲标而出之。时加省察也。
人而讲究画井之法。使九州之土无尺寸有遗。均乎颁民而无憾焉。则此谓先立乎其大者也。其些小不足者。行当逐手下落。而来教所谓以天下之大一国之富。何患无区处馀民之所者。诚为不易之论也。周礼所谓工贾閒民之流。无乃为是之故欤。然则此与向所论田有馀而为之区处者。实相表里。则恐亦不必预为定说以嫌临时从长之权。未知如何。至于来教有曰周礼以比闾族党之聚。居其民而统之有纪。以井夫丘甸之画。分其民而养之有方。以农圃虞牧闲民之职。授其民而处之有所。统之有纪。故民献其数而不敢自漏。养之有方。故民献其身而不敢自脱。处之有所。故民献其力而不敢自逸。又曰先王周知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九职既分。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上尽其心。人竭其力。然而事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疾怨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此二条事理语意。卓然俱到。不惟治得其序。而措置之亦难及也。窃欲标而出之。时加省察也。问。苏氏学校贡举制。
夫学校贡举二者。乃养贤选能之地。化民成俗之本。为治之方。孰先乎此。而亦不独此之为也。又得道则治。失道则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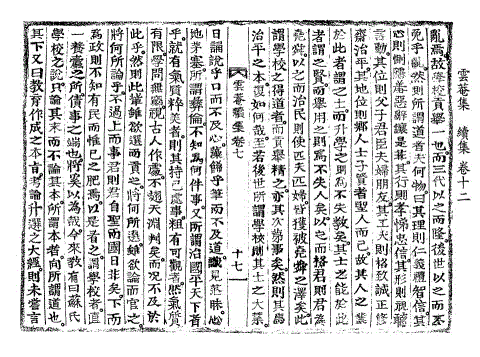 乱焉。故学校贡举一也。而三代以之而隆。后世以之而不免乎乱。然则所谓道者夫何物。曰其理则仁义礼智信。其心则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其行则孝悌忠信。其形则视听言动。其位则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其工夫则格致诚正修斋治平。其地位则乡人士子贤者圣人而已。故其人之业于此者谓之士。而升学之则为不失教矣。其士之能于此者谓之贤。而举用之则为不失人矣。以之而格君则君为尧舜。以之而治民则使匹夫匹妇。皆获被尧舜之泽矣。此谓学校之得道者。而贡举精之。亦其次第事矣。然则其为治平之本。复如何哉。至若后世所谓学校则其士之大业。日诵说乎口而不及心。藻饰乎笔而不及道。识见茫昧。心地茅塞。所谓彝伦。不知为何件事。又所谓治国平天下者乎。就有气质粹美者。则其持己处事。粗有可观者。然气质有限。学问无穷。视古人作处。不翅天渊判矣。而况不及于此乎。然则此辈虽欲选而贡之。将何所选。虽欲论而官之。将何所论乎。不过上而事君则君自圣而国日非矣。下而为政则不知有民而惟己之肥焉。以是看之。谓学校者。直一养蠹之所。债事之端也。将奚以为哉。今来教有曰苏氏学校之说。只论其末而不论其本。所谓本者。向所谓道也。其下又曰教育作成之本旨。考论升选之大经。则未尝言
乱焉。故学校贡举一也。而三代以之而隆。后世以之而不免乎乱。然则所谓道者夫何物。曰其理则仁义礼智信。其心则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其行则孝悌忠信。其形则视听言动。其位则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其工夫则格致诚正修斋治平。其地位则乡人士子贤者圣人而已。故其人之业于此者谓之士。而升学之则为不失教矣。其士之能于此者谓之贤。而举用之则为不失人矣。以之而格君则君为尧舜。以之而治民则使匹夫匹妇。皆获被尧舜之泽矣。此谓学校之得道者。而贡举精之。亦其次第事矣。然则其为治平之本。复如何哉。至若后世所谓学校则其士之大业。日诵说乎口而不及心。藻饰乎笔而不及道。识见茫昧。心地茅塞。所谓彝伦。不知为何件事。又所谓治国平天下者乎。就有气质粹美者。则其持己处事。粗有可观者。然气质有限。学问无穷。视古人作处。不翅天渊判矣。而况不及于此乎。然则此辈虽欲选而贡之。将何所选。虽欲论而官之。将何所论乎。不过上而事君则君自圣而国日非矣。下而为政则不知有民而惟己之肥焉。以是看之。谓学校者。直一养蠹之所。债事之端也。将奚以为哉。今来教有曰苏氏学校之说。只论其末而不论其本。所谓本者。向所谓道也。其下又曰教育作成之本旨。考论升选之大经。则未尝言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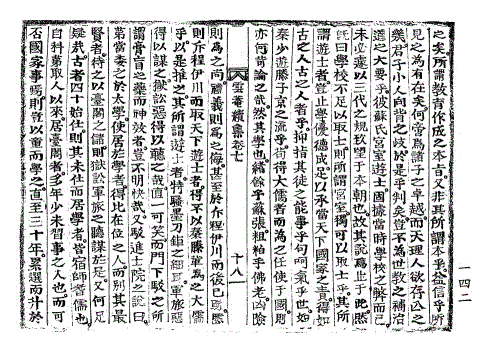 之矣。所谓教育作成之本旨。又非其所谓本乎。益信乎所见之为有在矣。何啻为诸子之卓越。而天理人欲存亡之几。君子小人向背之岐。于是乎判矣。岂不为世教之补治道之大要乎。彼苏氏宫室游士。固据当时学校之弊而已。未必遽以三代之规致望于本朝也。故其说为止于此。然既曰学校不足以取士。则所谓宫室。独可以取士乎。其所谓游士者。岂止学优德成。足以承当天下国家之责。得如古之人古之人者乎。抑指其徒之能事乎句呵气乎世。如秦少游滕子京之流乎。苟得大儒者而为之任使于国。则亦何苛论之哉。然其学也。绪馀乎苏张。粗粕乎佛老。凶险则为之尚。礼义则为之侮。甚至于斥程伊川而后已焉。然则斥程伊川而取天下游士者。得不以秦滕辈为之大儒乎。以是推之。其所谓游士者。特骚墨刀钜之细耳。军旅恶得以谋之。狱讼恶得以听之哉。直一可笑。而门下驳之所谓膏肓之药而神效者。岂不明快哉。又驳进士院之说曰。第当委之于太学。使居于学者。得比在位之人。而别其最贤者。待之以台阁之储。则狱讼军旅之听谋于是。又何足疑哉。古者四十始仕。则其未仕而居学者。皆宿师耆儒也。自科第取人以来。居台阁者。多年少未习事之人也。而可否国家事焉。则岂以童而学之。直至三十年。累选而升于
之矣。所谓教育作成之本旨。又非其所谓本乎。益信乎所见之为有在矣。何啻为诸子之卓越。而天理人欲存亡之几。君子小人向背之岐。于是乎判矣。岂不为世教之补治道之大要乎。彼苏氏宫室游士。固据当时学校之弊而已。未必遽以三代之规致望于本朝也。故其说为止于此。然既曰学校不足以取士。则所谓宫室。独可以取士乎。其所谓游士者。岂止学优德成。足以承当天下国家之责。得如古之人古之人者乎。抑指其徒之能事乎句呵气乎世。如秦少游滕子京之流乎。苟得大儒者而为之任使于国。则亦何苛论之哉。然其学也。绪馀乎苏张。粗粕乎佛老。凶险则为之尚。礼义则为之侮。甚至于斥程伊川而后已焉。然则斥程伊川而取天下游士者。得不以秦滕辈为之大儒乎。以是推之。其所谓游士者。特骚墨刀钜之细耳。军旅恶得以谋之。狱讼恶得以听之哉。直一可笑。而门下驳之所谓膏肓之药而神效者。岂不明快哉。又驳进士院之说曰。第当委之于太学。使居于学者。得比在位之人。而别其最贤者。待之以台阁之储。则狱讼军旅之听谋于是。又何足疑哉。古者四十始仕。则其未仕而居学者。皆宿师耆儒也。自科第取人以来。居台阁者。多年少未习事之人也。而可否国家事焉。则岂以童而学之。直至三十年。累选而升于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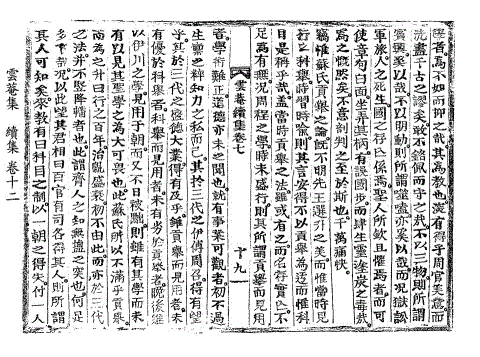 学者。为不如而抑之哉。其为教也。深有得乎周官美意。而洗尽千古之谬矣。敢不铭佩而守之哉。不以三物。则所谓宾兴。奚以哉。不以明动。则所谓噬嗑。亦奚以哉。而况狱讼军旅。人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圣人所钦且惧焉者。而可使章句白面。坐弄其柄。有误国步。而肆生灵涂炭之毒哉。为之慨然矣。不意剖判之至于斯也。千万痛快。
学者。为不如而抑之哉。其为教也。深有得乎周官美意。而洗尽千古之谬矣。敢不铭佩而守之哉。不以三物。则所谓宾兴。奚以哉。不以明动。则所谓噬嗑。亦奚以哉。而况狱讼军旅。人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圣人所钦且惧焉者。而可使章句白面。坐弄其柄。有误国步。而肆生灵涂炭之毒哉。为之慨然矣。不意剖判之至于斯也。千万痛快。窃惟苏氏贡举之论。既不明先王选升之美。而惟当时见行之科举。时习时喻。则其言安得不以贡举为迂而惟科目是称乎哉。盖当时贡举之法。虽或有之。而名存实亡。不足为有无。况周程之学。时未盛行。则其所谓贡举而见用者。学术难正。道德亦未之闻也。就有事业可观者。初不过生禀之粹知力之私而已。其于三代之伊傅周召。得有望乎。其于三代之盛德大业。得有及乎。虽贡举而见用者。未有优于科举者。科举而见用者。未有劣于贡举者。晚后虽以伊川之学。见用于朝。而又不日被黜。则虽有其学而未有以见其圣学之为大可畏也。此苏氏所以不满乎贡举。而为之升曰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而亦于三代之法。并不竖降幡者也。此谓齐人之知无盐之突也。何足多下哉。况以此望其君相曰百官有司各得其人。则所谓其人可知矣。来教有曰科目之制。以一朝之得失。付一人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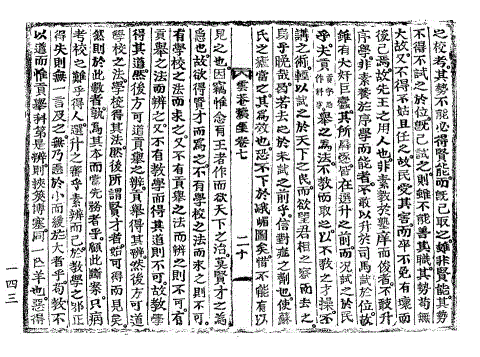 之校考。其势不能必得贤能。而既已取之。虽非贤能。其势不得不试之于位。既已试之。则虽不能善其职。其势苟无大故。又不得不姑且任之。故民受其害。而卒不免有坏而后已焉。故先王之用人也。非素教于塾庠而俊者。不敢升序学。非素养于序学而能者。不敢以升于司马试于位。故虽有大奸巨蠹。其所屏逐。皆在选升之前。而况试之于民乎。夫贡(贡字恐作科字。)举之为法。不教而取之。以不教之才操。不讲之术。轻以试之于天下之民。而欲望君相之察而去之。乌乎晚哉。曷若去之于未试之前乎。信对症之剂也。使苏氏之疟当之。其为效也。恐不下于峨嵋图矣。惜不能有以见之也。因窃惟念有王者作而欲天下之治。莫贤才之为急也。故欲得贤才而为之。不有学校之法而求之则不可。有学校之法而求之。又不有贡举之法而辨之则不可。有贡举之法而辨之。又不有教学而得其道则不可。故教学得其道。然后方可道贡举之辨。贡举得其辨。然后方可道学校之法。学校得其法。然后所谓贤才者。始可得而见矣。然则于此数者。孰为其本而当先务者乎。顾此断案。只病考校之难乎得人。选升之审乎素辨而已。于教学之邪正得失则无一言及之。无乃急于小而缓于大者乎。苟教不以道而惟贡举科第是辨。则挟筴博塞。同一亡羊也。恶得
之校考。其势不能必得贤能。而既已取之。虽非贤能。其势不得不试之于位。既已试之。则虽不能善其职。其势苟无大故。又不得不姑且任之。故民受其害。而卒不免有坏而后已焉。故先王之用人也。非素教于塾庠而俊者。不敢升序学。非素养于序学而能者。不敢以升于司马试于位。故虽有大奸巨蠹。其所屏逐。皆在选升之前。而况试之于民乎。夫贡(贡字恐作科字。)举之为法。不教而取之。以不教之才操。不讲之术。轻以试之于天下之民。而欲望君相之察而去之。乌乎晚哉。曷若去之于未试之前乎。信对症之剂也。使苏氏之疟当之。其为效也。恐不下于峨嵋图矣。惜不能有以见之也。因窃惟念有王者作而欲天下之治。莫贤才之为急也。故欲得贤才而为之。不有学校之法而求之则不可。有学校之法而求之。又不有贡举之法而辨之则不可。有贡举之法而辨之。又不有教学而得其道则不可。故教学得其道。然后方可道贡举之辨。贡举得其辨。然后方可道学校之法。学校得其法。然后所谓贤才者。始可得而见矣。然则于此数者。孰为其本而当先务者乎。顾此断案。只病考校之难乎得人。选升之审乎素辨而已。于教学之邪正得失则无一言及之。无乃急于小而缓于大者乎。苟教不以道而惟贡举科第是辨。则挟筴博塞。同一亡羊也。恶得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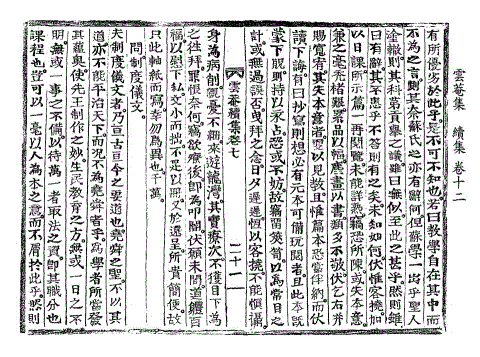 有所优劣于此乎。是不可不知也。若曰教学自在其中而不为之言。则其奈苏氏之亦有辞何。但苏学一出乎圣人涂辙。则其科第贡举之议。虽曰无似。至此之甚乎。然则虽曰有辞。其不患乎不答则有之矣。未知如何。伏惟客挠。加以日课。所示篇一再阅览。未能详熟。窃恐所陈。或失本意。兼之毫秃楮艰。累品以幅。粗画以书。类多不敬。伏乞右并赐宽宥。其失本意者。更以见教。且惟篇本恐当伴纳。而伏读下诲。有曰抄写则想必有元本可备玩阅者。且此本既蒙下贶。则持以永占。恐或不妨。故窃留筴笥。以为常目之计。或无过误否。曳拜之念。日夕迟迟。恒以客挠。不能慎摄。身为病削。亲忧不细。来游龙湾。其实疗次。不获目下为之往拜。罪恨奈何。窃欲疗后。既为叩阍。伏愿未间。道体百福。以慰下私。文小而拙。不足以册。又于远呈。所贵简便。故只此轴纸而写。幸勿为异也。千万。
有所优劣于此乎。是不可不知也。若曰教学自在其中而不为之言。则其奈苏氏之亦有辞何。但苏学一出乎圣人涂辙。则其科第贡举之议。虽曰无似。至此之甚乎。然则虽曰有辞。其不患乎不答则有之矣。未知如何。伏惟客挠。加以日课。所示篇一再阅览。未能详熟。窃恐所陈。或失本意。兼之毫秃楮艰。累品以幅。粗画以书。类多不敬。伏乞右并赐宽宥。其失本意者。更以见教。且惟篇本恐当伴纳。而伏读下诲。有曰抄写则想必有元本可备玩阅者。且此本既蒙下贶。则持以永占。恐或不妨。故窃留筴笥。以为常目之计。或无过误否。曳拜之念。日夕迟迟。恒以客挠。不能慎摄。身为病削。亲忧不细。来游龙湾。其实疗次。不获目下为之往拜。罪恨奈何。窃欲疗后。既为叩阍。伏愿未间。道体百福。以慰下私。文小而拙。不足以册。又于远呈。所贵简便。故只此轴纸而写。幸勿为异也。千万。问。制度仪文。
夫制度仪文者。乃亘古亘今之要道也。尧舜之圣。不以其道。亦不能平治天下。而况不为尧舜者乎。为学者所当发其蕴奥。使先王制作之妙。生民教育之方。无或一日之不明。无或一事之不备。以待万一者取法之资。即其职分也课程也。岂可以一毫以人为本之意。而不屑于此乎。然则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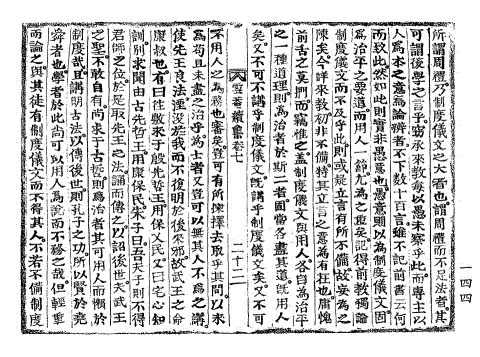 所谓周礼。乃制度仪文之大者也。谓周礼而不足法者。其可谓后学之言乎。窃承来教每以愚未察乎此。而专主以人为本之意为论辨者。不下数十百言。虽不记前书云何而致此。然如此则实非愚意也。愚意则以为制度仪文。固为治平之要道。而用人一节。尤为之重矣。记得前教独论制度仪文而不及乎此。则或疑立言有所不备。故妄为之陈矣。今详来教。初非不备。特其立言之意为有在也。庸愧前舌之莫扪。而窃惟之。盖制度仪文与用人。各自为治平之一种道理。则为治者于斯二者。固当各尽其道。既用人矣。又不可不讲乎制度仪文。既讲乎制度仪文矣。又不可不用人之为务也审矣。岂可有所拣择去取乎其间。以求为苟且未尽之治乎。为士者又岂可以无其人不为之讲。使先王良法。湮没于我而不复明于后来邪。故武王之命康叔也。有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朱子曰。吾夫子则不得君师之位。于是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夫武王之圣。不敢自有。尚求于古哲。则为治者其可用人而懒于制度哉。且讲明古法。以传后世。则孔子之功。所以贤于尧舜者也。学者于此尚可以用人为说而不务之哉。但轻重而论之。与其徒有制度仪文而不得其人。不若不备制度
所谓周礼。乃制度仪文之大者也。谓周礼而不足法者。其可谓后学之言乎。窃承来教每以愚未察乎此。而专主以人为本之意为论辨者。不下数十百言。虽不记前书云何而致此。然如此则实非愚意也。愚意则以为制度仪文。固为治平之要道。而用人一节。尤为之重矣。记得前教独论制度仪文而不及乎此。则或疑立言有所不备。故妄为之陈矣。今详来教。初非不备。特其立言之意为有在也。庸愧前舌之莫扪。而窃惟之。盖制度仪文与用人。各自为治平之一种道理。则为治者于斯二者。固当各尽其道。既用人矣。又不可不讲乎制度仪文。既讲乎制度仪文矣。又不可不用人之为务也审矣。岂可有所拣择去取乎其间。以求为苟且未尽之治乎。为士者又岂可以无其人不为之讲。使先王良法。湮没于我而不复明于后来邪。故武王之命康叔也。有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朱子曰。吾夫子则不得君师之位。于是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夫武王之圣。不敢自有。尚求于古哲。则为治者其可用人而懒于制度哉。且讲明古法。以传后世。则孔子之功。所以贤于尧舜者也。学者于此尚可以用人为说而不务之哉。但轻重而论之。与其徒有制度仪文而不得其人。不若不备制度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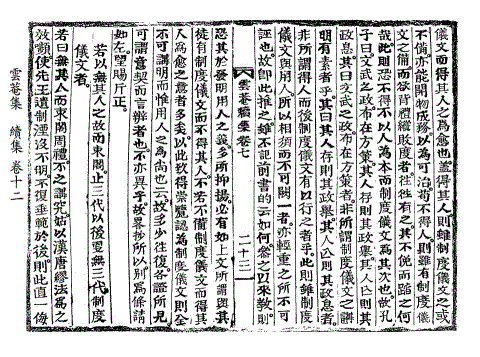 仪文而得其人之为愈也。盖得其人。则虽制度仪文之或不备。亦能开物成务。以为可治。苟不得人。则虽有制度仪文之备。而欲背礼纵败度者。往往有之。其不俛而蹈之何哉。此则恐不得不以人为本而制度仪文为其次也。故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非所谓制度仪文之讲明有素者乎。其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者。非所谓得人而后制度仪文有以行之者乎。此则虽制度仪文与用人。所以相须而不可阙一者。亦轻重之所不可诬也。故即此推之。虽不记前书的云如何。参之以来教。则恐其于发明用人之义。多所抑扬。必有如上文所谓与其徒有制度仪文而不得其人。不若不备制度仪文而得其人为愈之意者多矣。以此致得崇览认为制度仪文则全不可讲明而惟用人之为尚也云。故多少往复。各證所见。可谓意契而言辨者也。不亦异乎。故略抄所以。别为条请如左。望赐斤正。
仪文而得其人之为愈也。盖得其人。则虽制度仪文之或不备。亦能开物成务。以为可治。苟不得人。则虽有制度仪文之备。而欲背礼纵败度者。往往有之。其不俛而蹈之何哉。此则恐不得不以人为本而制度仪文为其次也。故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非所谓制度仪文之讲明有素者乎。其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者。非所谓得人而后制度仪文有以行之者乎。此则虽制度仪文与用人。所以相须而不可阙一者。亦轻重之所不可诬也。故即此推之。虽不记前书的云如何。参之以来教。则恐其于发明用人之义。多所抑扬。必有如上文所谓与其徒有制度仪文而不得其人。不若不备制度仪文而得其人为愈之意者多矣。以此致得崇览认为制度仪文则全不可讲明而惟用人之为尚也云。故多少往复。各證所见。可谓意契而言辨者也。不亦异乎。故略抄所以。别为条请如左。望赐斤正。若以无其人之故而束阁。止三代以后更无三代制度仪文者。
若曰无其人而束阁周礼。不之讲究。姑以汉唐缪法为之效嚬。使先王遗制湮没不明。不复垂范于后。则此直一侮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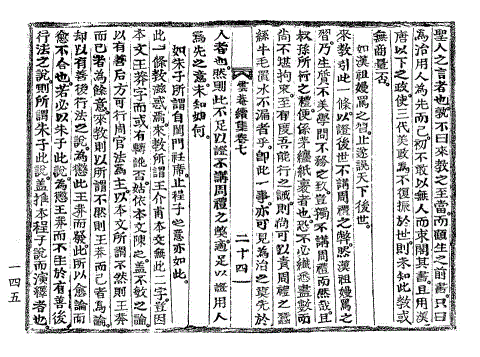 圣人之言者也。孰不曰来教之至当。而顾生之前书。只曰为治用人为先而已。初不敢以无人而束阁其书。且用汉唐以下之政。使三代美政为不复振于世。则未知此教或无商量否。
圣人之言者也。孰不曰来教之至当。而顾生之前书。只曰为治用人为先而已。初不敢以无人而束阁其书。且用汉唐以下之政。使三代美政为不复振于世。则未知此教或无商量否。如汉祖嫚骂之习。止遂误天下后世。
来教引此一条。以證后世不讲周礼之弊。然汉祖嫚骂之习。乃生质不美学问不务之致。岂独不讲周礼而然哉。且叔孙所行之礼。便系茅缠纸裹者也。恐不必纤悉尽数而尚不堪拘束。至有度吾能行之诫。则尚可以责周礼之蚕丝牛毛置水不漏者乎。即此一事。亦可见为治之莫先于人者也。然则此不足以證不讲周礼之弊。适足以證用人为先之意。未知如何。
如朱子所谓自闺门衽席。止程子之意亦如此。
此一条教滋惑焉。来教所谓王介甫本文无此二字。岂因本文王莽字而或有转讹否。姑依本文陈之。盖不敏之论。以有善后方可行周官法为主。以本文所谓不然则王莽而已者为馀意。来教则以所谓不然则王莽而已者为论。却以有善后行法之说。为惩此王莽而发。此所以愈论而愈不合也。若必以朱子此说。为惩王莽而不主于有善后行法之说。则所谓朱子此说。盖推本程子说而演绎者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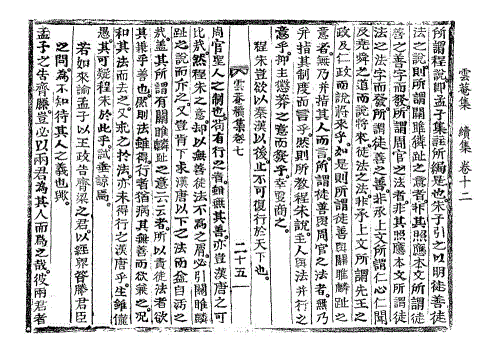 所谓程说。即孟子集注所编是也。朱子引之以明徒善徒法之说。则所谓关雎獜趾之意者。非其照应本文所谓徒善之善字而发。所谓周官之法者。非其照应本文所谓徒法之法字而发。所谓徒善之善。非承上文所谓仁心仁闻及尧舜之道而说将来。徒法之法。非承上文所谓先王之政及仁政而说将来乎。如是则所谓徒善与关雎麟趾之意者。无乃并指其人而言。所谓徒善与周官之法者。无乃并指其制度而言乎。然则所教程朱说。主人与法并行之意乎。抑主惩莽之意而发乎。幸更商之。
所谓程说。即孟子集注所编是也。朱子引之以明徒善徒法之说。则所谓关雎獜趾之意者。非其照应本文所谓徒善之善字而发。所谓周官之法者。非其照应本文所谓徒法之法字而发。所谓徒善之善。非承上文所谓仁心仁闻及尧舜之道而说将来。徒法之法。非承上文所谓先王之政及仁政而说将来乎。如是则所谓徒善与关雎麟趾之意者。无乃并指其人而言。所谓徒善与周官之法者。无乃并指其制度而言乎。然则所教程朱说。主人与法并行之意乎。抑主惩莽之意而发乎。幸更商之。程朱岂欲以秦汉以后。止不可复行于天下也。
周官圣人之制也。苟有行之者。虽无其善。亦岂汉唐之可比哉。然程朱之意。却以无善徒法不为之屑。必引关雎麟趾之说而斥之。又岂肯下求汉唐以下之法而益自污之哉。盖其所谓有关雎麟趾之意云云者。所以责徒法者欲其兼乎善也。然则法虽得。行者犹病其无善而欲兼之。况和其法而去之。又求之于法。亦未得行之汉唐乎。生虽儱愚。其可疑程朱于此乎。试垂谅焉。
若如来谕孟子以王政告齐梁之君。以经界答滕君臣之问。为不知待其人之义也欤。
孟子之告齐滕。岂必以两君为其人而为之哉。彼两君者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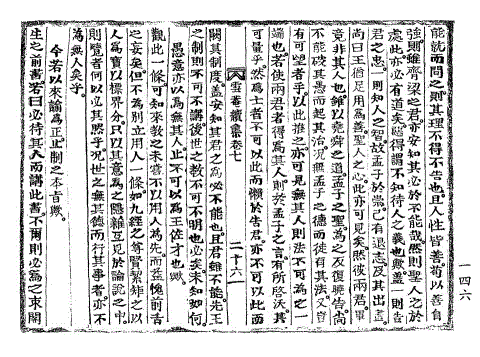 能就而问之。则其理不得不告也。且人性皆善。苟以善自强。则虽齐梁之君。亦安知其必于不能哉。然则圣人之于处此。亦必有道矣。恶得谓不知待人之义也欤。盖一则告君之忠。一则知人之智。故孟子于崇。已有退志。及其出画。尚曰王犹足用为善。圣人之心。此亦可见矣。然彼两君。毕竟非其人也。虽以尧舜之道。孟子之圣。为之反复晓告。尚不能破其愚而起其治。况无孟子之德而徒有其法。又岂有可望者乎。以此推之。亦可见无其人则法不可为之一端也。若使两君者得为其人。则于孟子之言。有所启沃。其可量乎。然为士者不可以此而懒于告君。亦不可以此而阙其制度。盖安知其君之为必不能也。且君虽不能。先王之制则不可不讲。后世之教不可不明也必矣。未知如何。
能就而问之。则其理不得不告也。且人性皆善。苟以善自强。则虽齐梁之君。亦安知其必于不能哉。然则圣人之于处此。亦必有道矣。恶得谓不知待人之义也欤。盖一则告君之忠。一则知人之智。故孟子于崇。已有退志。及其出画。尚曰王犹足用为善。圣人之心。此亦可见矣。然彼两君。毕竟非其人也。虽以尧舜之道。孟子之圣。为之反复晓告。尚不能破其愚而起其治。况无孟子之德而徒有其法。又岂有可望者乎。以此推之。亦可见无其人则法不可为之一端也。若使两君者得为其人。则于孟子之言。有所启沃。其可量乎。然为士者不可以此而懒于告君。亦不可以此而阙其制度。盖安知其君之为必不能也。且君虽不能。先王之制则不可不讲。后世之教不可不明也必矣。未知如何。愚意亦以为无其人。止不可以为王佐才也欤。
观此一条。可知来教之未尝不以用人为先。而益愧前舌之妄矣。但不为别立用人一条。如九经之尊贤絜矩之以人为宝以标界分。只以其意为之隐杂互见于论说之中。则览者何以必其然乎。况世之无其德而行其事者。亦不为无人矣乎。
今若以来谕为正。止制之本旨欤。
生之前书。若曰必待其人而讲此书。不尔则必为之束阁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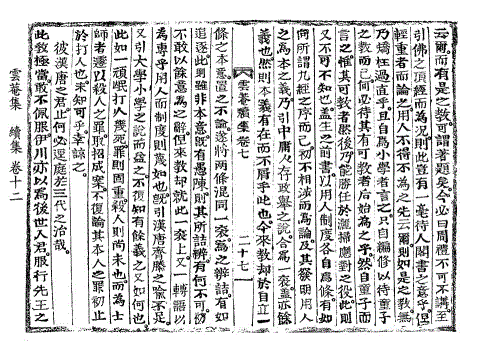 云尔。而有是之教。可谓著题矣。今必曰周礼不可不讲。至引佛之顶经而为况。则此岂有一毫待人阁书之意乎。但轻重者而论之。用人不得不为之先云尔。则如是之教。无乃矫枉过直乎。且自为小学者言之。只自编修以待童子之教而已。何必待其有可教者后始为之乎。然自童子而言之。惟其可教者然后。乃能胜任于洒扫应对之役。此则又不可不知也。盖生之前书。以用人制度各自为条。有如向所谓九经之序而已。初不相涉而为论。及其发明用人之为本之义。乃引中庸人存政举之说。合为一衮。盖亦馀义也。然则本义有在而不屑乎此也。今来教却于自立一条之本意。置之不论。遂将两条混同一衮。为之辨诘。有如追逐。此则虽非本意。既有愚陈。则其所诘辨。有何不可。初不敢以馀意为之辞。但来教却就此一衮上。又一转语以为专乎用人而制度则蔑如也。既引汉唐齐滕之喻不足。又引大学小学之说而益之。不复知有馀义之又如何也。此如一顽氓打人几死。罪则固重。杀人则尚未也。而为士师者遽以杀人之罪。取招成案。不复论其本人之罪初止于打人也。未知可乎。幸谅之。
云尔。而有是之教。可谓著题矣。今必曰周礼不可不讲。至引佛之顶经而为况。则此岂有一毫待人阁书之意乎。但轻重者而论之。用人不得不为之先云尔。则如是之教。无乃矫枉过直乎。且自为小学者言之。只自编修以待童子之教而已。何必待其有可教者后始为之乎。然自童子而言之。惟其可教者然后。乃能胜任于洒扫应对之役。此则又不可不知也。盖生之前书。以用人制度各自为条。有如向所谓九经之序而已。初不相涉而为论。及其发明用人之为本之义。乃引中庸人存政举之说。合为一衮。盖亦馀义也。然则本义有在而不屑乎此也。今来教却于自立一条之本意。置之不论。遂将两条混同一衮。为之辨诘。有如追逐。此则虽非本意。既有愚陈。则其所诘辨。有何不可。初不敢以馀意为之辞。但来教却就此一衮上。又一转语以为专乎用人而制度则蔑如也。既引汉唐齐滕之喻不足。又引大学小学之说而益之。不复知有馀义之又如何也。此如一顽氓打人几死。罪则固重。杀人则尚未也。而为士师者遽以杀人之罪。取招成案。不复论其本人之罪初止于打人也。未知可乎。幸谅之。彼汉唐之君。止何必径庭于三代之治哉。
此教极当。敢不佩服。伊川亦以为后世人君。服行先王之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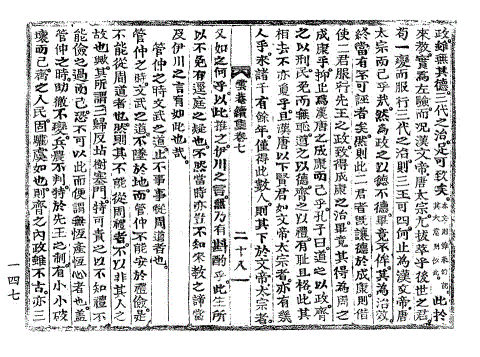 政。虽无其德。三代之治。足可致矣。(本文则虽未的记。其大意则似此。)此于来教。实为左验。而况汉文帝,唐太宗。尤拔萃乎后世之君。苟一变而服行三代之治。则三王可四。何止为汉文帝,唐太宗而已乎哉。然为政之以德不德。毕竟不侔。其为治效。终当有不可诬者矣。然则此二君者既让德于成康。则借使二君服行先王之政。致得成康之治。毕竟其得为周之成康乎。抑止为汉唐之成康而已乎。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其相去不亦夐乎。且汉唐以下贤君如文帝,太宗者。亦有几人乎。求诸千有馀年。仅得此数人。则其下于文帝,太宗者。又如之何乎。以此推之。伊川之言。无乃有斟酌乎。此生所以不免有径庭之疑也。不然当时亦岂不知来教之谛当及伊川之言有如此也哉。
政。虽无其德。三代之治。足可致矣。(本文则虽未的记。其大意则似此。)此于来教。实为左验。而况汉文帝,唐太宗。尤拔萃乎后世之君。苟一变而服行三代之治。则三王可四。何止为汉文帝,唐太宗而已乎哉。然为政之以德不德。毕竟不侔。其为治效。终当有不可诬者矣。然则此二君者既让德于成康。则借使二君服行先王之政。致得成康之治。毕竟其得为周之成康乎。抑止为汉唐之成康而已乎。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其相去不亦夐乎。且汉唐以下贤君如文帝,太宗者。亦有几人乎。求诸千有馀年。仅得此数人。则其下于文帝,太宗者。又如之何乎。以此推之。伊川之言。无乃有斟酌乎。此生所以不免有径庭之疑也。不然当时亦岂不知来教之谛当及伊川之言有如此也哉。管仲之时文武之道。止不事事从周道者也。
管仲之时。文武之道。不坠于地。而管仲不能安于礼俭。是不能从周道者也。然则其不能从周礼者。不以非其人之故也欤。其所谓三归反坫树塞门。特可责之以不知礼不能俭之过而已。恐不可以此而便谓无恒产恒心者也。盖管仲之时。助彻不变。兵农不判。特于先王之制。有小小破坏而已。齐之人民。固驩虞如也。则齐之内政虽不古。亦三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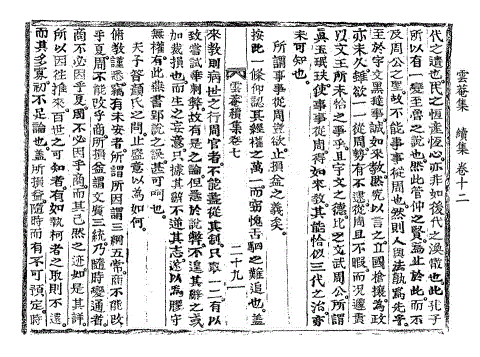 代之遗也。民之恒产恒心。亦非如后代之涣散也。此孔子所以有一变至鲁之说也。然此管仲之贤。为止于此。而不及周公之圣。故不能事事从周也。然则人与法孰为先乎。至于宇文黑獭事。诚如来教。然究以言之。立国枪攘。为政亦未久。虽欲一一从周。势有不逮。从周且不暇。而况遽责以文王所未恰之事乎。且宇文之德。比之文武周公。所谓真玉珉玞。使事事从周。得如来教。其能恰似三代之治。亦未可知也。
代之遗也。民之恒产恒心。亦非如后代之涣散也。此孔子所以有一变至鲁之说也。然此管仲之贤。为止于此。而不及周公之圣。故不能事事从周也。然则人与法孰为先乎。至于宇文黑獭事。诚如来教。然究以言之。立国枪攘。为政亦未久。虽欲一一从周。势有不逮。从周且不暇。而况遽责以文王所未恰之事乎。且宇文之德。比之文武周公。所谓真玉珉玞。使事事从周。得如来教。其能恰似三代之治。亦未可知也。所谓事事从周岂欲。止损益之义矣。
按此一条仰认其经权之万一。而窃愧舌驷之难追也。盖来教则病世之行周官者。不能尽从其制。只取一二。有以致尝试乖剌弊。故有是之论。但急于说弊。不遑其辞之或加裁损也。而生之妄意。只据其辞不逆其志。遂以为胶守无权。有此燕书郢说之误。甚可呵也。
夫子答颜氏之问。止盛意以为如何。
俯教谨悉。窃有未安者。所谓所因谓三纲五常。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乃随时变通者。商不必因乎夏。周不必因乎商。而其已然之迹。如是其详。所以因往推来。百世之可知者。有如执柯者之取则不远。而其多寡。初不足论也。盖所损益。随时而有不可预定。时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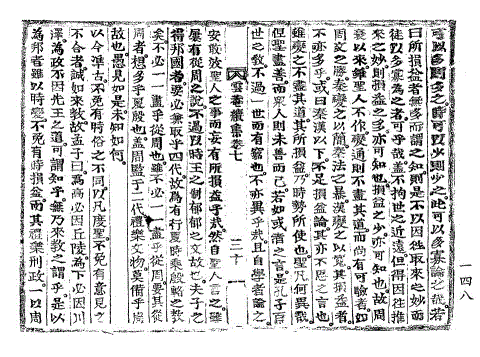 可以多则多之。时可以少则少之。此可以多寡论之哉。若曰所损益者无多而谓之知。则是不以因往取来之妙而徒以多寡为之者。可乎哉。盖不拘世之近远。但得因往推来之妙。则损益之多。亦可知也。损益之少。亦可知也。故周衰以来。虽圣人不作。变通则不尽其道。而尚有可验者。如周文之胜。秦变之以简。秦法之暴。汉变之以宽。其损益者。不亦多乎。或曰秦汉以下。不足损益论。其亦不思之言也。虽变之不尽其道。其所损益。乃时势所使也。圣凡何异哉。但圣尽善。而众人则未善而已。若如或者之言。是孔子百世之教。不过一世而有穷也。不亦异乎哉。且自学者论之。安敢效圣人之事而妄有所损益乎哉。然自圣人言之。虽屡有从周之说。不过以时王之制郁郁之文故也。夫子之得邦国者。要必兼取乎四代。故为有行夏时乘殷辂之教矣。不必一一尽乎从周也。虽不必一一尽乎从周。要其从周者。想多乎夏殷也。盖周监于二代。礼乐文物。莫备乎周故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可以多则多之。时可以少则少之。此可以多寡论之哉。若曰所损益者无多而谓之知。则是不以因往取来之妙而徒以多寡为之者。可乎哉。盖不拘世之近远。但得因往推来之妙。则损益之多。亦可知也。损益之少。亦可知也。故周衰以来。虽圣人不作。变通则不尽其道。而尚有可验者。如周文之胜。秦变之以简。秦法之暴。汉变之以宽。其损益者。不亦多乎。或曰秦汉以下。不足损益论。其亦不思之言也。虽变之不尽其道。其所损益。乃时势所使也。圣凡何异哉。但圣尽善。而众人则未善而已。若如或者之言。是孔子百世之教。不过一世而有穷也。不亦异乎哉。且自学者论之。安敢效圣人之事而妄有所损益乎哉。然自圣人言之。虽屡有从周之说。不过以时王之制郁郁之文故也。夫子之得邦国者。要必兼取乎四代。故为有行夏时乘殷辂之教矣。不必一一尽乎从周也。虽不必一一尽乎从周。要其从周者。想多乎夏殷也。盖周监于二代。礼乐文物。莫备乎周故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以今准古。不免有时俗之不同。以凡度圣。不免有意见之不合者。诚如来教。故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知乎。无乃来教之谓乎。是以为邦者虽以时变。不免有时损益。而其礼乐刑政。一以周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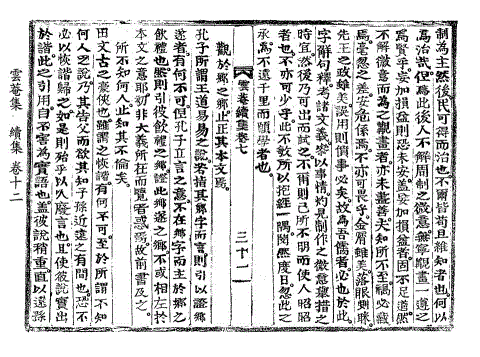 制为主然后。民可得而治也。不尔皆苟且维知者也。何以为治哉。但为此后人不解周制之微意。无宁觏画一遵之为贤乎。妄加损益则恐未安。盖妄加损益者。固不足道。然不解微意而为之觏画者。亦未尽善。夫知所不至。祸必藏焉。毫忽之差。安危系焉。不亦可畏乎。金屑虽美。落眼则眯。先王之政虽美。误用则偾事必矣。故为吾儒者。必也于此。字解句释。考诸文义。参以事情。灼见制作之微意举措之时宜。然后乃可出而试之。不尔则己所不明而使人昭昭者也。不亦可少乎。此不敏所以抱经一隅。闵然度日。忽此之承。为不远千里而愿学者也。
制为主然后。民可得而治也。不尔皆苟且维知者也。何以为治哉。但为此后人不解周制之微意。无宁觏画一遵之为贤乎。妄加损益则恐未安。盖妄加损益者。固不足道。然不解微意而为之觏画者。亦未尽善。夫知所不至。祸必藏焉。毫忽之差。安危系焉。不亦可畏乎。金屑虽美。落眼则眯。先王之政虽美。误用则偾事必矣。故为吾儒者。必也于此。字解句释。考诸文义。参以事情。灼见制作之微意举措之时宜。然后乃可出而试之。不尔则己所不明而使人昭昭者也。不亦可少乎。此不敏所以抱经一隅。闵然度日。忽此之承。为不远千里而愿学者也。观于乡之乡。止正其本文焉。
孔子所谓王道易易之说。若指其乡字而言。则引以證乡遂者。有何不可。但孔子立言之意。不在乡字而主于乡之饮礼也。然则引彼饮礼之乡。證此乡遂之乡。不或相左于本文之意耶。初非大义所在而览者惑焉。故前书及之。
所不知何人。止知其不伦矣。
田文古之豪侠也。虽谓之恢谐。有何不可。至于所谓不知何人之说。乃其告父而欲其知子孙近远之有间也。恐不必以恢谐归之。如是则殆乎以人废言也。且使彼说实出于谐。此之引用。自不害为实语也。盖彼说稍重。直以远孙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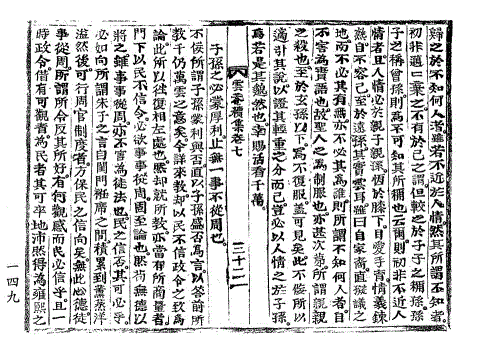 归之于不知何人者。虽若不近于人情。然其所谓不知者。初非迈迈弃之。不有于己之谓。但较之于子子之称孙。孙子之称曾孙。则为不可知其所称也云尔。则初非不近人情者。且人情必于亲子亲孙。恒于膝下。目爱手育。情义鍊熟。自不容已。至于远孙。其实云耳。虽曰自家裔。直拟议之地。而不必其有无。亦不必其为谁。则所谓不知何人者。自不害为实语也。故圣人之为制服也。亦甚次第。所谓亲亲之杀也。至于玄孙以下。为不复服。盖可见矣。此不佞所以适引其说。以證其轻重之分而已。岂必以人情之于子孙。为若是其邈然也。幸赐活看千万。
归之于不知何人者。虽若不近于人情。然其所谓不知者。初非迈迈弃之。不有于己之谓。但较之于子子之称孙。孙子之称曾孙。则为不可知其所称也云尔。则初非不近人情者。且人情必于亲子亲孙。恒于膝下。目爱手育。情义鍊熟。自不容已。至于远孙。其实云耳。虽曰自家裔。直拟议之地。而不必其有无。亦不必其为谁。则所谓不知何人者。自不害为实语也。故圣人之为制服也。亦甚次第。所谓亲亲之杀也。至于玄孙以下。为不复服。盖可见矣。此不佞所以适引其说。以證其轻重之分而已。岂必以人情之于子孙。为若是其邈然也。幸赐活看千万。子孙之必蒙厚利。止无一事不从周也。
不佞所谓子孙蒙利与否。直以子孙盛否为言。以答前所教千仍万云之意矣。今详来教。却以民不信政令之致为论。此所以往复相左处也。然却就所教。亦当有所商量者。门下以民不信令。必欲事事从周。固至论也。然苟无德以将之。虽事事从周。亦不害为徒法也。民之信否。其可必乎。必如向所谓朱子之言自闺门衽席之间。积累到薰蒸洋溢然后。可行周官制度者。方保民之信向矣。无此心德。徒事从周。所谓所令反其所好。有何观感而民必信乎。且一时政令。借有可观者。为民者其可卒地沛然得为雍熙之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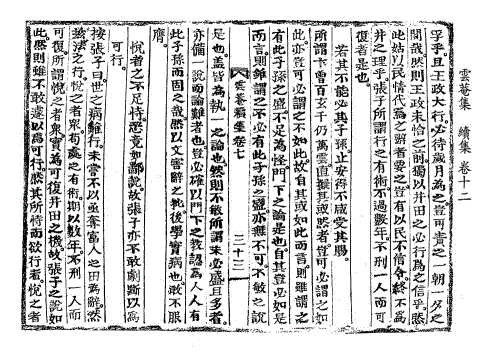 孚乎。且王政大行。必待岁月为之。岂可责之一朝一夕之间哉。然则王政未恰之前。独以井田之必行为之信乎。然此姑以民情代为之辞者要之。岂有以民不信令。终不为井之理乎。张子所谓行之有术。不过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者是也。
孚乎。且王政大行。必待岁月为之。岂可责之一朝一夕之间哉。然则王政未恰之前。独以井田之必行为之信乎。然此姑以民情代为之辞者要之。岂有以民不信令。终不为井之理乎。张子所谓行之有术。不过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者是也。若其不能必其子孙。止安得不咸受其赐。
所谓十曾百玄千仍万云。直拟其或然者。岂可必谓之如此。亦岂可必谓之不如此。故自其或如此而言。则虽谓之有此子孙之盛。不足为怪。门下之论是也。自其岂必如是而言。则虽谓之不必有此子孙之盛。亦无不可。不敏之说是也。盖皆为执一之论也。然则不敏所谓未必盛且多者。亦备一说而论难者也。岂必确以门下之教认为人人有此子孙而固之哉。然以文害辞之批。后学实病也。敢不服膺。
悦者之不足恃。恐竟如鄙说。故张子亦不敢剧断以为可行。
按张子曰。世之病难行。未尝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玆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谓悦之者众。实为可复井田之机。故张子之说如此。然则虽不敢遽以为可行。然其所恃而欲行者。悦之者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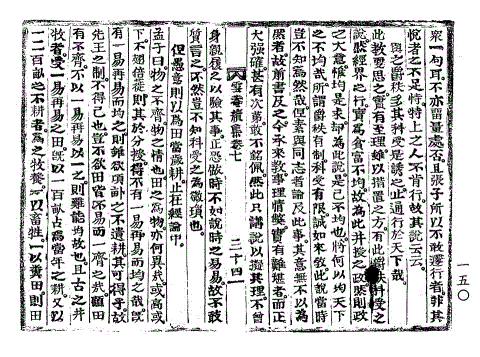 众一句耳。不亦留量处否。且张子所以不敢遽行者。非其悦者之不足恃。特上之人不肯行。故其说云云。
众一句耳。不亦留量处否。且张子所以不敢遽行者。非其悦者之不足恃。特上之人不肯行。故其说云云。与之爵秩多其科受是诱之。止通行于天下哉。
此教更思之。实有至理。虽以措置之方。有此爵秩科受之说。然经界之行。实为贫富不均。故为此井授之政。然则政之大意。惟均是求。却为此说。是已不均也。将何以均天下之不均哉。所谓爵秩有制。科受有限。诚如来教。此说当时岂不知为然哉。但素与同志者论及此事。其意无不以为然者。故前书及之。今承来教。事理情弊。实有难堪者。而正大强确。甚有次第。敢不铭佩。然此只讲说以拟其理。不曾身亲履之以验其事。正恐做时不如说时之易易。故不敢质言之。不然岂不知科受之为微琐也。
但愚意则以为田当岁耕。止在经论中。
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田之为物。亦何异哉。或高或下。不翅倍蓰。则其于分授。得不有一易再易而均之哉。既有一易再易而均之。则虽欲顷亩之不遗耕。其可得乎。故先王之制。不得已也。岂不欲田皆不易而一齐之哉。顾田有不齐。不以一易再易以一之。则难能均故也。且古之井牧者。受一易再易之田。既以一百亩占为当年之耕。又以一二百亩之不耕者。为之牧养。一以畜牲。一以粪田。则田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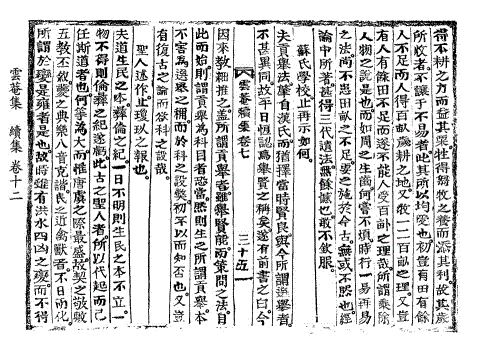 得不耕之力而益其粟。牲得刍牧之养而添其利。故其岁所收者。不让于不易者。此其所以均受也。初岂有田有馀人不足而人得百亩岁耕之地。又牧一二百亩之理。又岂有人有馀田不足而遂不能人受百亩之理哉。所谓乘除人物之说是也。而如周之生齿。何尝不烦。时行一易再易之法。尚不患田亩之不足。要之施于今古。无或不然也。经论中所著。甚得三代遗法。无馀憾也。敢不钦服。
得不耕之力而益其粟。牲得刍牧之养而添其利。故其岁所收者。不让于不易者。此其所以均受也。初岂有田有馀人不足而人得百亩岁耕之地。又牧一二百亩之理。又岂有人有馀田不足而遂不能人受百亩之理哉。所谓乘除人物之说是也。而如周之生齿。何尝不烦。时行一易再易之法。尚不患田亩之不足。要之施于今古。无或不然也。经论中所著。甚得三代遗法。无馀憾也。敢不钦服。苏氏学校。止再示如何。
夫贡举法。肇自汉氏。而犹择当时贤良。与今所谓选举者。不甚异同。故平日恒认为举贤之称矣。遂有前书之白。今因来教细推之。盖所谓贡举者。虽举贤能。而策问之法。自此而始。则谓贡举为科目者恐当。然则生之所谓贡举。本不害为选举之称。而于科之设弊。初不以而知否也。又岂有复古之论而欲科之设哉。
圣人述作。止琼玖之报也。
夫道生民之本。彝伦之纪。一日不明则生民之本不立。一物不得则伦彝之纪遂亏。此古之圣人者。所以代起而己任斯道者也。何等为大。而惟唐虞之际最盛。故契之敬敷五教丕叙。夔之典乐八音克谐。民之近禽兽者。不日而化。所谓于变是雍者是也。故时虽有洪水四凶之变。而不得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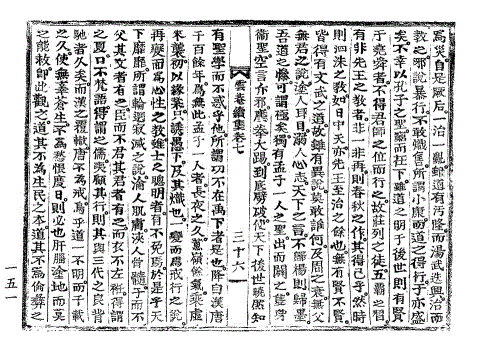 为灾。自是厥后。一治一乱。虽道有污隆。而汤武迭兴。治而教之。邪说暴行。不敢炽售。所谓小康。而道之得行。于亦盛矣。不幸以孔子之圣。穷而在下。虽道之明于后世则有贤于尧舜者。不得君师之位而行之。故庄列之徒。五霸之习。有非先王之教者。非一非再。则春秋之作。其得已乎。然时则泗洙之教。如日中天。亦先王至治之馀也。无有贤不贤。皆得有文武之道。故虽有异说。莫敢谁何。及周之衰。无父无君之说。涂人耳目。溺人心志。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吾道之惨。可谓极矣。独有孟子一人之圣。出而辟之。只身卫圣。空言斥邪。粗拳大踢。到底劈破。使天下后世晓然知有圣学而不惑乎他。所谓功不在禹下者是也。降自汉唐千百馀年。为无此孟子一人者。长夜之久。葱岭馀气。乘虚来袭。初以缘业。只诱愚下。及其炽也。一变而为戒行之说。再变而为心性之教。虽士之聪明者。有不免焉。于是乎天下靡靡。所谓轮回寂灭之说。沦人肌肤。浃人骨髓。子而不父其文(一作父)者有之。臣而不君其君者有之。而衣不左衽。得谓之夏。口不梵语。得谓之儒。夷顾其行。则其与三代之良背驰者久矣。而汉之覆辙。唐不为戒。乌乎道一不明。而千载之久。使无辜苍生。不为愁恨度日。则必也肝脑涂地而莫之能救。即此观之。道其不为生民之本。道其不为伦彝之
为灾。自是厥后。一治一乱。虽道有污隆。而汤武迭兴。治而教之。邪说暴行。不敢炽售。所谓小康。而道之得行。于亦盛矣。不幸以孔子之圣。穷而在下。虽道之明于后世则有贤于尧舜者。不得君师之位而行之。故庄列之徒。五霸之习。有非先王之教者。非一非再。则春秋之作。其得已乎。然时则泗洙之教。如日中天。亦先王至治之馀也。无有贤不贤。皆得有文武之道。故虽有异说。莫敢谁何。及周之衰。无父无君之说。涂人耳目。溺人心志。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吾道之惨。可谓极矣。独有孟子一人之圣。出而辟之。只身卫圣。空言斥邪。粗拳大踢。到底劈破。使天下后世晓然知有圣学而不惑乎他。所谓功不在禹下者是也。降自汉唐千百馀年。为无此孟子一人者。长夜之久。葱岭馀气。乘虚来袭。初以缘业。只诱愚下。及其炽也。一变而为戒行之说。再变而为心性之教。虽士之聪明者。有不免焉。于是乎天下靡靡。所谓轮回寂灭之说。沦人肌肤。浃人骨髓。子而不父其文(一作父)者有之。臣而不君其君者有之。而衣不左衽。得谓之夏。口不梵语。得谓之儒。夷顾其行。则其与三代之良背驰者久矣。而汉之覆辙。唐不为戒。乌乎道一不明。而千载之久。使无辜苍生。不为愁恨度日。则必也肝脑涂地而莫之能救。即此观之。道其不为生民之本。道其不为伦彝之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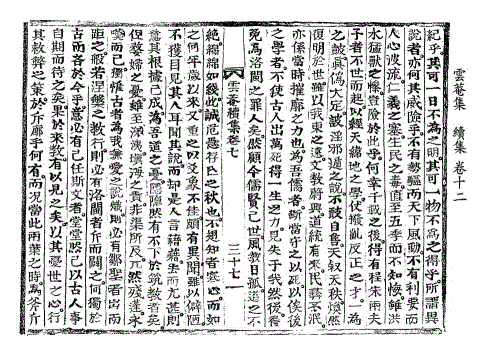 纪乎。其可一日不为之明。其可一物不为之得乎。所谓异说者。亦何其威险乎。不有势驱而天下风动。不有利要而人心波流。仁义之塞。生民之毒。直至五季而不知悔。虽洪水猛兽之惨。岂险于此乎。何幸千载之后。得有程朱两夫子者不世而起。以经天纬地之学。仗拨乱反正之才。一为之鼓。真伪大定。诐淫邪遁之说。不敢自售。天叙天秩。焕然复明于世。虽以我东之远。文教蔚兴。道统有来。民彝不泯。亦系当时摧廓之力也。为吾儒者。断当守之以死。以俟后之学者。不使古人出万死得一生之力。见失于我然后。得免为洛闽之罪人矣。然顾今儒贤已世。风教日孤。道之不绝。绵绵如线。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不翅知者寒心。而如之何年岁以来。又重之以爻象不佳。颇有异闻。虽以僻陋。不获目见其人耳闻其说。而却是人言藉藉。去而尤甚。则意其根据已成。为吾道之忧。隐隐然有不下于筑教者矣。但婺妇(嫠妇)之忧。虽至涕洟。填海之责。非渠所及。兀然残蓬。永叹而已。独惟古者为我兼爱之说炽。则必有邹圣者出而距之。般若涅槃之教行。则必有洛闽者斥而辟之。何独于古而吝于今乎。意必有己任斯文者。堂堂然已以古人事自期而待之矣。果于来教。有以见之矣。以其忧世之心。行其救弊之策。于斥廓乎何有。而况当此两叶之时。为斧斤
纪乎。其可一日不为之明。其可一物不为之得乎。所谓异说者。亦何其威险乎。不有势驱而天下风动。不有利要而人心波流。仁义之塞。生民之毒。直至五季而不知悔。虽洪水猛兽之惨。岂险于此乎。何幸千载之后。得有程朱两夫子者不世而起。以经天纬地之学。仗拨乱反正之才。一为之鼓。真伪大定。诐淫邪遁之说。不敢自售。天叙天秩。焕然复明于世。虽以我东之远。文教蔚兴。道统有来。民彝不泯。亦系当时摧廓之力也。为吾儒者。断当守之以死。以俟后之学者。不使古人出万死得一生之力。见失于我然后。得免为洛闽之罪人矣。然顾今儒贤已世。风教日孤。道之不绝。绵绵如线。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不翅知者寒心。而如之何年岁以来。又重之以爻象不佳。颇有异闻。虽以僻陋。不获目见其人耳闻其说。而却是人言藉藉。去而尤甚。则意其根据已成。为吾道之忧。隐隐然有不下于筑教者矣。但婺妇(嫠妇)之忧。虽至涕洟。填海之责。非渠所及。兀然残蓬。永叹而已。独惟古者为我兼爱之说炽。则必有邹圣者出而距之。般若涅槃之教行。则必有洛闽者斥而辟之。何独于古而吝于今乎。意必有己任斯文者。堂堂然已以古人事自期而待之矣。果于来教。有以见之矣。以其忧世之心。行其救弊之策。于斥廓乎何有。而况当此两叶之时。为斧斤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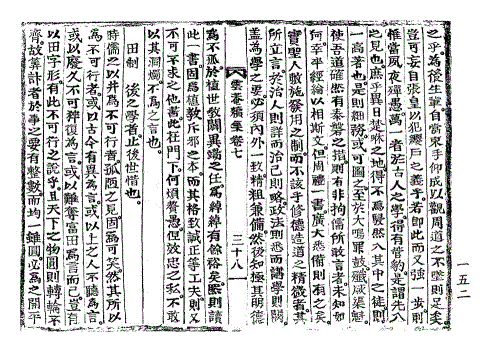 之乎。为后生辈。自当束手仰成以观周道之不坠则足矣。岂可妄自张皇以犯缨户之义乎。若即此而又强一步。则惟当夙夜殚愚。万一者于古人之学。得有管豹。是谓先入之见也。庶乎异日楚咻之地。得不为骎然入其中之徒。则一高著也。是则细务。或可图之。至于大鸣罪鼓。歼厥渠魁。使吾道确然有泰磐之措。则有非拘儒所敢言者。未知如何。幸卒经纶以相斯文。但周礼一书。广大悉备则有之矣。实圣人敷施发用之制。而不该乎修德造道之精微者。其所立言。于治人则详而治己则略。政法则悉而讲学则阙。盖为学之要。必须内外一致。精粗兼备。然后知极其明德为不孤。于植世教辟异端之任。为绰绰有馀裕矣。然则读此一书。固为植教斥邪之本。而其格致诚正等工夫。则又不可不求之他书。此在门下。何烦赘愚。但效忠之私。不敢以其洞烛。不为之言也。
之乎。为后生辈。自当束手仰成以观周道之不坠则足矣。岂可妄自张皇以犯缨户之义乎。若即此而又强一步。则惟当夙夜殚愚。万一者于古人之学。得有管豹。是谓先入之见也。庶乎异日楚咻之地。得不为骎然入其中之徒。则一高著也。是则细务。或可图之。至于大鸣罪鼓。歼厥渠魁。使吾道确然有泰磐之措。则有非拘儒所敢言者。未知如何。幸卒经纶以相斯文。但周礼一书。广大悉备则有之矣。实圣人敷施发用之制。而不该乎修德造道之精微者。其所立言。于治人则详而治己则略。政法则悉而讲学则阙。盖为学之要。必须内外一致。精粗兼备。然后知极其明德为不孤。于植世教辟异端之任。为绰绰有馀裕矣。然则读此一书。固为植教斥邪之本。而其格致诚正等工夫。则又不可不求之他书。此在门下。何烦赘愚。但效忠之私。不敢以其洞烛。不为之言也。田制 后之学者。止后世惜也。
时儒之以井为不可行者。孤陋之见。固为可笑。然其所以为不可行者。或以古今有异为言。或以上之人不听为言。或以废久不可猝复为言。或以难夺富田为言而已。岂有以田字形。有此不可行之说乎。且天下之物圆则转轮不齐。故算计者于事之要有整数。而均一虽圆。必为之开平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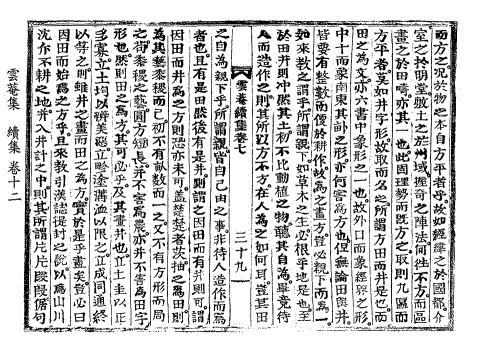 而方之。况于物之本自方平者乎。故如经纬之于国都。介室之于明堂。敷土之于州域。握奇之阵法。何往不方。而区画之于田畴。亦其一也。此固理势而既方之。取则九区而方平者。莫如井字形。故取而名之。所谓方田而井是也。而田之为文。亦六书中象形之一也。故外口而象经界之形。中十而象南东其亩之形。亦何害为方也。但无论田与井。皆要有整数而便于耕作。故为之画方。岂必亲下而为一。如来教之谓乎。所谓亲下。如草木之生。必根乎地是也。至于田井则冲然其土。初不比动植之物。听其自为。毕竟待人而造作之。则其所以方不方。在人为之如何耳。岂其田之自为亲下乎。所谓亲。皆自己由之事。非待人造作而为者也。且有是田然后有是井。则谓之因田而有井则可。谓因田而井为之方则恐亦未可。盖楚楚者茨。抽之为田。则为其艺黍稷而已。初不有亩数而一之。又不有方形而局之。苟黍稷之艺。圆方短长。并不害为农。亦并不害为田字形也。然则田之为方。其可必乎。及其画井也。立土圭以正多寡。立土均以辨美恶。立畛涂沟洫以限之。立成同通终以等之。则虽井之画而田之为方。实于是乎尽矣。岂必曰因田而始为之方乎。且来教引汉志提封之说。以为山川沈斥不耕之地。并入井计之中。则其所谓片片段段。倨句
而方之。况于物之本自方平者乎。故如经纬之于国都。介室之于明堂。敷土之于州域。握奇之阵法。何往不方。而区画之于田畴。亦其一也。此固理势而既方之。取则九区而方平者。莫如井字形。故取而名之。所谓方田而井是也。而田之为文。亦六书中象形之一也。故外口而象经界之形。中十而象南东其亩之形。亦何害为方也。但无论田与井。皆要有整数而便于耕作。故为之画方。岂必亲下而为一。如来教之谓乎。所谓亲下。如草木之生。必根乎地是也。至于田井则冲然其土。初不比动植之物。听其自为。毕竟待人而造作之。则其所以方不方。在人为之如何耳。岂其田之自为亲下乎。所谓亲。皆自己由之事。非待人造作而为者也。且有是田然后有是井。则谓之因田而有井则可。谓因田而井为之方则恐亦未可。盖楚楚者茨。抽之为田。则为其艺黍稷而已。初不有亩数而一之。又不有方形而局之。苟黍稷之艺。圆方短长。并不害为农。亦并不害为田字形也。然则田之为方。其可必乎。及其画井也。立土圭以正多寡。立土均以辨美恶。立畛涂沟洫以限之。立成同通终以等之。则虽井之画而田之为方。实于是乎尽矣。岂必曰因田而始为之方乎。且来教引汉志提封之说。以为山川沈斥不耕之地。并入井计之中。则其所谓片片段段。倨句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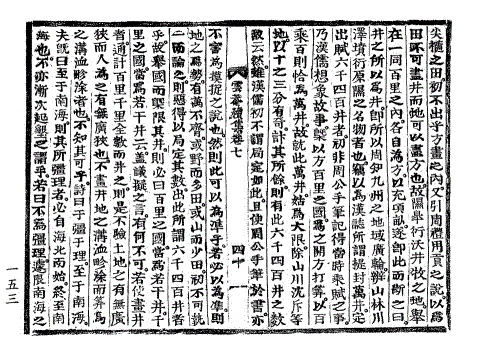 尖椭之田。初不出乎方画之内。又引周礼用贡之说。以为田不可尽井而地可以尽方也。故隰皋衍沃井牧之地。举在一同百里之内。各自为方。以充顷亩。遂既此而断之曰。井之所以为井。即所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辨山林川泽坟衍原隰之名物者也。窃以为汉志所谓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者。初非周公手笔记得当时乘赋之事。乃汉儒想象故事。槩以方百里之国。为之开方打算。以百乘百则恰为万井。故就此万井。姑为大限。除山川沈斥等地。以十之三分有奇。计其所馀。则有此六千四百井之数故云然。虽汉儒初不谓局定如此。且使周公手笔于书。亦不害为摸捉之说也。然则此可以为准乎。若必以为准。则地之为势。有万不齐。或野而多田。或山而少田。初不可执一而论之。则恶得以局定其数。出此所谓六千四百井者乎。故举国而槩限其井。则必曰百里之国。当为若干井。千里之国。当为若干井云。盖议拟之言。有何不可。若使画井者。通计百里千里全数而井之。则是不验土地之有无广狭而人为之有无广狭也。不画井地之沟洫畛涂而算为之沟洫畛涂者也。不知其可乎。诗曰于彊于理。至于南海。夫既曰至于南海。则其所彊理者。必自海北而始。终至南海也。不亦渐次起垦之谓乎。若曰不为彊理。遽限南海之
尖椭之田。初不出乎方画之内。又引周礼用贡之说。以为田不可尽井而地可以尽方也。故隰皋衍沃井牧之地。举在一同百里之内。各自为方。以充顷亩。遂既此而断之曰。井之所以为井。即所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辨山林川泽坟衍原隰之名物者也。窃以为汉志所谓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者。初非周公手笔记得当时乘赋之事。乃汉儒想象故事。槩以方百里之国。为之开方打算。以百乘百则恰为万井。故就此万井。姑为大限。除山川沈斥等地。以十之三分有奇。计其所馀。则有此六千四百井之数故云然。虽汉儒初不谓局定如此。且使周公手笔于书。亦不害为摸捉之说也。然则此可以为准乎。若必以为准。则地之为势。有万不齐。或野而多田。或山而少田。初不可执一而论之。则恶得以局定其数。出此所谓六千四百井者乎。故举国而槩限其井。则必曰百里之国。当为若干井。千里之国。当为若干井云。盖议拟之言。有何不可。若使画井者。通计百里千里全数而井之。则是不验土地之有无广狭而人为之有无广狭也。不画井地之沟洫畛涂而算为之沟洫畛涂者也。不知其可乎。诗曰于彊于理。至于南海。夫既曰至于南海。则其所彊理者。必自海北而始。终至南海也。不亦渐次起垦之谓乎。若曰不为彊理。遽限南海之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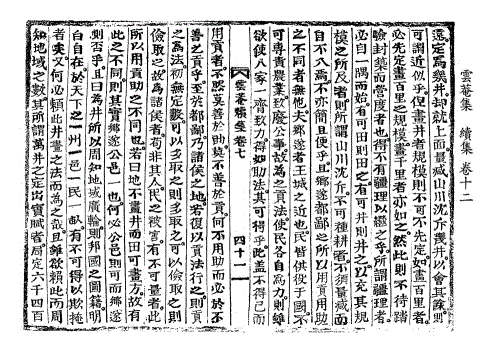 远。定为几井。却就上面。量减山川沈斥几井。以会其馀。则可谓近似乎。但画井者规模则不可不先定。如画百里者。必先定画百里之规模。画千里者亦如之。然此则不待踏验封筑而营度者也。得不有疆理以继之乎。所谓疆理者。必自一隅而始。有可田则田之。有可井则井之。以充其规模之所及者。则所谓山川沈斥。不可种耕者。不须量减而自不入焉。不亦简且便乎。且乡遂都鄙之所以用贡用助之不同者无他。夫乡遂者王城之近也。民皆供役于国。不可专责农业。致废公事。故为之贡法。使民各自为力。则虽欲使八家一齐致力。得如助法。其可得乎。此盖不得已而用贡者。不然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何不用助而必于不善之贡乎。至于都鄙。乃诸侯之地。若复以贡法行之。则贡之为法。初无定数。可以多取之则多取之。可以俭取之则俭取之。故为诸侯者。苟非其人。民之被害。有不可量者。此所以用贡助之不同也。若曰地不画井而田可画方。故有此之不同。则其实乡遂公邑一也。何必公邑则可而乡遂则否乎。且曰为井所以周知地域广轮。则邦国之图籍。明白自在。于天下之一州一邑一民一亩。有不可得以欺掩者矣。又何必赖此井画之法而为之哉。且虽欲赖此而周知地域之数。其所谓万井之定出实赋者。局定六千四百
远。定为几井。却就上面。量减山川沈斥几井。以会其馀。则可谓近似乎。但画井者规模则不可不先定。如画百里者。必先定画百里之规模。画千里者亦如之。然此则不待踏验封筑而营度者也。得不有疆理以继之乎。所谓疆理者。必自一隅而始。有可田则田之。有可井则井之。以充其规模之所及者。则所谓山川沈斥。不可种耕者。不须量减而自不入焉。不亦简且便乎。且乡遂都鄙之所以用贡用助之不同者无他。夫乡遂者王城之近也。民皆供役于国。不可专责农业。致废公事。故为之贡法。使民各自为力。则虽欲使八家一齐致力。得如助法。其可得乎。此盖不得已而用贡者。不然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何不用助而必于不善之贡乎。至于都鄙。乃诸侯之地。若复以贡法行之。则贡之为法。初无定数。可以多取之则多取之。可以俭取之则俭取之。故为诸侯者。苟非其人。民之被害。有不可量者。此所以用贡助之不同也。若曰地不画井而田可画方。故有此之不同。则其实乡遂公邑一也。何必公邑则可而乡遂则否乎。且曰为井所以周知地域广轮。则邦国之图籍。明白自在。于天下之一州一邑一民一亩。有不可得以欺掩者矣。又何必赖此井画之法而为之哉。且虽欲赖此而周知地域之数。其所谓万井之定出实赋者。局定六千四百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4L 页
 井而加减不得乎。毕竟国国不同。邑邑相殊。恶得以此而算之哉。故其治井之必自一处而渐次起功者。遂人职曰。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小司徒之职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此虽有贡助之不同。亦可以傍取兼照。有以见当时画井之必自一处而始。不为通千百里之全数而为除减。有如汉志者矣。不是周公手笔。而求诸事理。皆有实验者乎。且所教田不可尽井而地可以尽方。故一主乎方。无论平野长谷。一以方画之。虽不满百亩者。如犁鐴头镰子曲者。尽数开录。以业馀夫。使奸窦不售其所谋为则缜密莫如。可谓发前哲所未发者。非穷究极好之至。何以有此哉。但按古之画井者。于沟洫广轮之间。莫不正正翼翼。以取均平方整之数。故为之用贡则必曰夫间有遂。遂上有经。一如向所陈者。为之助者。必曰九夫为井。井间有沟。方十里为成。成间有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古之人所以方田者。不已极乎。盖自一夫至万夫。自一里而至方百里者。等级绝严。数目均适。上之下之。不敢有毫忽
井而加减不得乎。毕竟国国不同。邑邑相殊。恶得以此而算之哉。故其治井之必自一处而渐次起功者。遂人职曰。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小司徒之职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此虽有贡助之不同。亦可以傍取兼照。有以见当时画井之必自一处而始。不为通千百里之全数而为除减。有如汉志者矣。不是周公手笔。而求诸事理。皆有实验者乎。且所教田不可尽井而地可以尽方。故一主乎方。无论平野长谷。一以方画之。虽不满百亩者。如犁鐴头镰子曲者。尽数开录。以业馀夫。使奸窦不售其所谋为则缜密莫如。可谓发前哲所未发者。非穷究极好之至。何以有此哉。但按古之画井者。于沟洫广轮之间。莫不正正翼翼。以取均平方整之数。故为之用贡则必曰夫间有遂。遂上有经。一如向所陈者。为之助者。必曰九夫为井。井间有沟。方十里为成。成间有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古之人所以方田者。不已极乎。盖自一夫至万夫。自一里而至方百里者。等级绝严。数目均适。上之下之。不敢有毫忽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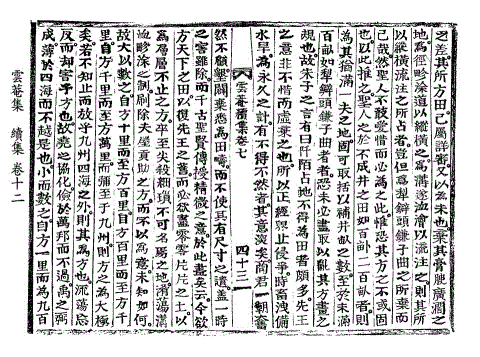 之差。其所方田。已属详审。又以为未也。弃其膏腴广阔之地。为径畛涂道以纵横之。为沟遂洫浍以流注之。则其所以纵横流注之所占者。岂但为犁鐴头镰子曲之所弃而已哉。然圣人不敢爱惜而必为之此。惟恐其方之不或固也。以此推之。圣人之于不成井之田如百亩二百亩者。则为其犹满一夫之地。固可取括以补井亩之数。至于未满百亩如犁鐴头镰子曲者者。恐未必尽取以乱其方画之规也。故朱子之言有曰阡陌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一朝奋然不顾。垦辟弃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云。今欲方天下之田。以复先王之旧。而必欲尽零零片片之土。以为层层不止之方。卒至尖杀细琐不可名焉之地。淆荡沟洫畛涂之制。刷除夫屋贡助之方。而不以为意。未知如何。故大以数之。自方十里而至方百里。自方百里而至方千里。自方千里而至方万里。而弥至于九州。则方之为大极矣。若不知止而放乎九州四海之外。则其为方也。流荡忘反。而却害乎方也。故尧之协化。俭于万邦而不过。禹之弼成。薄于四海而不越是也。小而数之。自方一里而为九百
之差。其所方田。已属详审。又以为未也。弃其膏腴广阔之地。为径畛涂道以纵横之。为沟遂洫浍以流注之。则其所以纵横流注之所占者。岂但为犁鐴头镰子曲之所弃而已哉。然圣人不敢爱惜而必为之此。惟恐其方之不或固也。以此推之。圣人之于不成井之田如百亩二百亩者。则为其犹满一夫之地。固可取括以补井亩之数。至于未满百亩如犁鐴头镰子曲者者。恐未必尽取以乱其方画之规也。故朱子之言有曰阡陌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一朝奋然不顾。垦辟弃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云。今欲方天下之田。以复先王之旧。而必欲尽零零片片之土。以为层层不止之方。卒至尖杀细琐不可名焉之地。淆荡沟洫畛涂之制。刷除夫屋贡助之方。而不以为意。未知如何。故大以数之。自方十里而至方百里。自方百里而至方千里。自方千里而至方万里。而弥至于九州。则方之为大极矣。若不知止而放乎九州四海之外。则其为方也。流荡忘反。而却害乎方也。故尧之协化。俭于万邦而不过。禹之弼成。薄于四海而不越是也。小而数之。自方一里而为九百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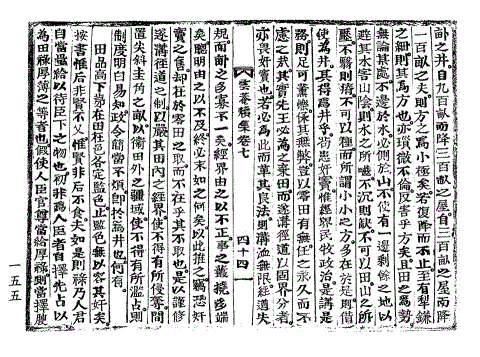 亩之井。自九百亩而降三百亩之屋。自三百亩之屋而降一百亩之夫。则方之为小极矣。若复降而不止。至有犁镰之细。则其为方也。亦琐微不伦。反害乎方矣。且田之为势。无论某处。不边于水。必侧于山。不使有一边剩馀之地以避其水害山阴。则水之所啮。不沉则缺。不可以田。山之所压。不翳则瘠。不可以种。而所谓小小之方。多在于是。则借使为井。其得为井乎。苟患奸窦。惟经界民牧政治。是讲是务。则足可薰烁。保其无弊。岂以零田有无。任之永久而不虑之哉。其实先王必为之弃田。而遂沟径道以固界分者。亦畏奸窦也。若必为此而革其良法。则沟洫无限。经道失规。而亩之多寡不一矣。经界由之以不正。事之䕺挠多端矣。聪明由之以不及。终必末如之何矣。以此推之。窃恐奸窦之售。却在于零田之取。而不在乎其不取也。是以谨修遂沟径道之制。以严其田内之经界。使不得有所侵夺。间置尖斜圭角之亩。以卫田外之疆域。使不得有所滥占。则制度明白易知。政令简当不烦。即于为井也。何有。
亩之井。自九百亩而降三百亩之屋。自三百亩之屋而降一百亩之夫。则方之为小极矣。若复降而不止。至有犁镰之细。则其为方也。亦琐微不伦。反害乎方矣。且田之为势。无论某处。不边于水。必侧于山。不使有一边剩馀之地以避其水害山阴。则水之所啮。不沉则缺。不可以田。山之所压。不翳则瘠。不可以种。而所谓小小之方。多在于是。则借使为井。其得为井乎。苟患奸窦。惟经界民牧政治。是讲是务。则足可薰烁。保其无弊。岂以零田有无。任之永久而不虑之哉。其实先王必为之弃田。而遂沟径道以固界分者。亦畏奸窦也。若必为此而革其良法。则沟洫无限。经道失规。而亩之多寡不一矣。经界由之以不正。事之䕺挠多端矣。聪明由之以不及。终必末如之何矣。以此推之。窃恐奸窦之售。却在于零田之取。而不在乎其不取也。是以谨修遂沟径道之制。以严其田内之经界。使不得有所侵夺。间置尖斜圭角之亩。以卫田外之疆域。使不得有所滥占。则制度明白易知。政令简当不烦。即于为井也。何有。田品高下第在田在邑各定监色。止监色无以容其奸矣。
按书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夫如是则禄乃人君自当量给以待臣下之物也。初非为人臣者自择先占以为田禄厚薄之等者也。假使人臣官尊当给厚禄。则当择腴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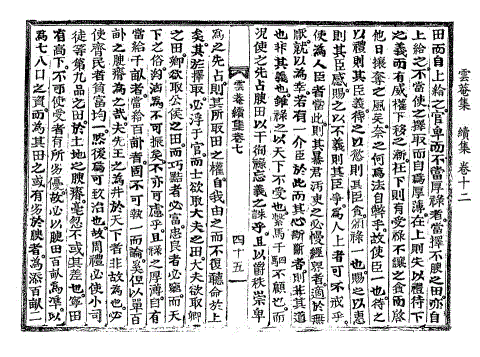 田而自上给之。官卑而不当厚禄者。当择不腴之田。亦自上给之。不当使之择取而自为厚薄。在上则失以礼待下之义而有威权下移之渐。在下则有受禄不让之贪而启他日攘夺之风矣。奈之何为法自弊乎。故使臣一也。待之以礼则其臣义。待之以欲则其臣贪。颁禄一也。赐之以惠则其臣感。赐之以不义则其臣争。为人上者可不戒乎。使为人臣者当此。则其暴君污吏之必慢经界者。适于无厌。就以为幸。若有一介臣于此而其心断断者。则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以天下不受也。系马千驷不顾也。而况使之先占腴田以干徇禄忘义之诛乎。且以爵秩崇卑为之先占。则其所取田之权。自我由之而不复听命于上矣。其于择取。必浮于官。而士欲取大夫之田。大夫欲取卿之田。卿欲取公侯之田。而巧黠者必富。忠良者必穷。而天下之俗。汹汹为不可振矣。不亦可虑乎。且禄之厚薄。自有当给千亩者。当给百亩者。固不可执一而论。奚但以单百亩之腴瘠为之哉。夫先王之为井于天下者非故为也。必使齐民者贫富均一。然后为可致治也。故周礼必使小司徒等第九品之田。于土地之腴瘠。毫忽不或其差也。宁田有高下。不可使受者有所劣优。故必以腴田百亩为准。以为七八口之资。而为其田之或有劣于腴者。为添百亩二
田而自上给之。官卑而不当厚禄者。当择不腴之田。亦自上给之。不当使之择取而自为厚薄。在上则失以礼待下之义而有威权下移之渐。在下则有受禄不让之贪而启他日攘夺之风矣。奈之何为法自弊乎。故使臣一也。待之以礼则其臣义。待之以欲则其臣贪。颁禄一也。赐之以惠则其臣感。赐之以不义则其臣争。为人上者可不戒乎。使为人臣者当此。则其暴君污吏之必慢经界者。适于无厌。就以为幸。若有一介臣于此而其心断断者。则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以天下不受也。系马千驷不顾也。而况使之先占腴田以干徇禄忘义之诛乎。且以爵秩崇卑为之先占。则其所取田之权。自我由之而不复听命于上矣。其于择取。必浮于官。而士欲取大夫之田。大夫欲取卿之田。卿欲取公侯之田。而巧黠者必富。忠良者必穷。而天下之俗。汹汹为不可振矣。不亦可虑乎。且禄之厚薄。自有当给千亩者。当给百亩者。固不可执一而论。奚但以单百亩之腴瘠为之哉。夫先王之为井于天下者非故为也。必使齐民者贫富均一。然后为可致治也。故周礼必使小司徒等第九品之田。于土地之腴瘠。毫忽不或其差也。宁田有高下。不可使受者有所劣优。故必以腴田百亩为准。以为七八口之资。而为其田之或有劣于腴者。为添百亩二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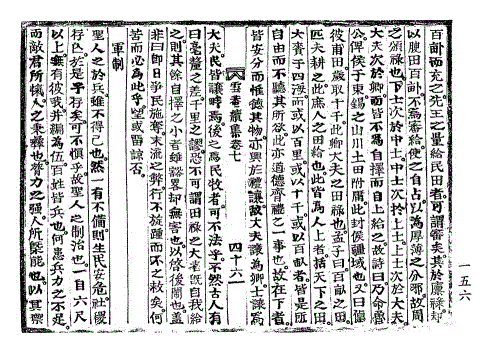 百亩而充之。先王之量给民田者。可谓审矣。其于廪禄。却以腴田百亩。不为审给。使之自占。以为厚薄之分邪。故周之颁禄也。下士次于中士。中士次于上士。上士次于大夫。大夫次于卿。而皆不为自择而自上给之。故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此封侯疆域也。又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此卿大夫之田禄也。孟子曰。百亩之田。匹夫耕之。此庶人之田给也。此皆为人上者。括天下之田。大赉于四海。而或以百里。或以十千。或以百亩者。皆是所自由而不听其所欲。此亦道德齐礼之一事也。故在下者。皆安分而惟德其物。亦兴于礼让。故大夫让为卿。士让为大夫。民皆让畔焉。后之为民牧者。可不法乎。不然古人有曰毫釐之差。千里之谬。恐不可谓田禄之大者既自我给之。则其馀自择之小者虽豁略却无害也。以启后闹也。盖非曰即日争民施夺。末流之弊。行不旋踵而不之救矣。何苦而必为此乎。望或留谅否。
百亩而充之。先王之量给民田者。可谓审矣。其于廪禄。却以腴田百亩。不为审给。使之自占。以为厚薄之分邪。故周之颁禄也。下士次于中士。中士次于上士。上士次于大夫。大夫次于卿。而皆不为自择而自上给之。故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此封侯疆域也。又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此卿大夫之田禄也。孟子曰。百亩之田。匹夫耕之。此庶人之田给也。此皆为人上者。括天下之田。大赉于四海。而或以百里。或以十千。或以百亩者。皆是所自由而不听其所欲。此亦道德齐礼之一事也。故在下者。皆安分而惟德其物。亦兴于礼让。故大夫让为卿。士让为大夫。民皆让畔焉。后之为民牧者。可不法乎。不然古人有曰毫釐之差。千里之谬。恐不可谓田禄之大者既自我给之。则其馀自择之小者虽豁略却无害也。以启后闹也。盖非曰即日争民施夺。末流之弊。行不旋踵而不之救矣。何苦而必为此乎。望或留谅否。军制
圣人之于兵。虽不得已也。然一有不备。则生民安危。社稷存亡。于是乎存矣。可不慎乎。故圣人之制治也。一自六尺以上。无有彼我。并编为伍。百姓皆兵也。何患兵力之不足。而敌君所忾。人之秉彝也。膂力之强。人所槩能也。以其御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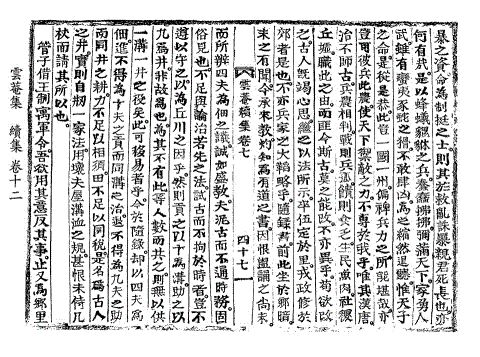 暴之资。命为制挺之士。则其于救乱诛暴亲君死长也。亦何有哉。是以蜂蚁貔貅之兵。蠢蠢拂拂。弥满天下。家勇人武。虽有蛮夷豕蛇之猾。不敢肆凶。为之缩然退听。惟天子之命。是从是恭。此岂一国一州。偏裨兵力之所能堪哉。亦岂可彼兵此农。使天下御敌之力。不专于我乎。唯其汉唐。治不师古。兵农相判。战则兵孤。馈则食乏。生民鱼肉。社稷丘墟。职此之由。而匪今斯古。莫之能改。不亦异乎。苟欲改之。古人既竭心思。继之以法所示。卒伍定于里。戎政修于郊者是也。不亦兵家之大韬略乎。随录书。前此坐于乡暗。未之有闻。今承来教。灼知为有道之书。因恨盥诵之尚未。而所辨四夫为佃之议。诚如盛教。夫泥古而不通时务。固俗见也。不足与论治若先之法。试古而不拘于时者。岂不遵以守之。以为丘川之因乎。然则贡之以十为沟。助之以九为井。非故为也。为其不有此等人数而共之。则无以供一沟一井之役矣。此可移易者乎。今于随录。却以四夫为佃。进不得为十夫之贡而同沟之治。退不得为九夫之助而同井之耕。力不足以相须。田不足以同税。是名为古人之井。实则自刱一家法。用坏夫屋沟洫之规。甚恨未侍几杖而请其所以也。
暴之资。命为制挺之士。则其于救乱诛暴亲君死长也。亦何有哉。是以蜂蚁貔貅之兵。蠢蠢拂拂。弥满天下。家勇人武。虽有蛮夷豕蛇之猾。不敢肆凶。为之缩然退听。惟天子之命。是从是恭。此岂一国一州。偏裨兵力之所能堪哉。亦岂可彼兵此农。使天下御敌之力。不专于我乎。唯其汉唐。治不师古。兵农相判。战则兵孤。馈则食乏。生民鱼肉。社稷丘墟。职此之由。而匪今斯古。莫之能改。不亦异乎。苟欲改之。古人既竭心思。继之以法所示。卒伍定于里。戎政修于郊者是也。不亦兵家之大韬略乎。随录书。前此坐于乡暗。未之有闻。今承来教。灼知为有道之书。因恨盥诵之尚未。而所辨四夫为佃之议。诚如盛教。夫泥古而不通时务。固俗见也。不足与论治若先之法。试古而不拘于时者。岂不遵以守之。以为丘川之因乎。然则贡之以十为沟。助之以九为井。非故为也。为其不有此等人数而共之。则无以供一沟一井之役矣。此可移易者乎。今于随录。却以四夫为佃。进不得为十夫之贡而同沟之治。退不得为九夫之助而同井之耕。力不足以相须。田不足以同税。是名为古人之井。实则自刱一家法。用坏夫屋沟洫之规。甚恨未侍几杖而请其所以也。管子借王制寓军令。吾欲用其意反其事。止又为乡里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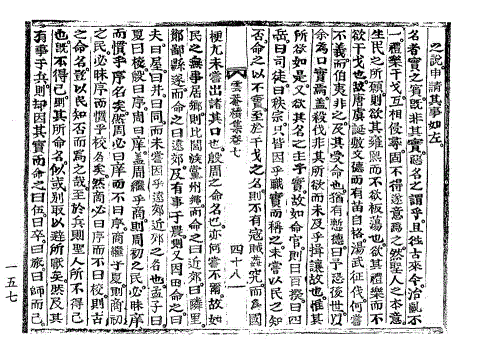 之说。申请其事如左。
之说。申请其事如左。名者实之宾。既非其实。恶名之谓乎。且往古来今。治乱不一。礼乐干戈。互相侵寻。固不得遂意为之。然圣人之本意。生民之所愿。则欲其雍熙而不欲板荡也。欲其礼乐而不欲干戈也。故唐虞诞敷文德而有苗自格。汤武征伐。何尝不义。而伯夷非之。及其受命也。犹有惭德。曰予恐后世。以余为口实焉。盖杀伐非其所欲而未及乎揖让故也。惟其所欲如是。又欲其名之主乎实。故如命官。则曰百揆。曰四岳。曰司徒。曰秩宗。只皆因乎职实而称之。未尝以民之知否。命之以不实。至于干戈之名。则不有寇贼奸究。而为国梗尤未尝出诸其口也。殷周之命名也。亦何尝不尔。故如民之无事居乡。则比闾族党州乡。而命之曰近郊。曰邻里。酂鄙县遂。而命之曰远郊。及有事于农。则又因田命之。曰夫。曰屋。曰井。曰同。而未尝因乎远郊近郊之名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盖周继乎商。则周初之民。必昧庠而惯乎序名矣。然周必曰庠而不曰序。商继乎夏。则商初之民。必昧序而惯乎校名矣。然商必曰序而不曰校。则古之命名。岂以民知否而为之哉。至于兵则圣人所不得已也。既不得已。则其所命名。似或别取以避所厌矣。然及其有事于兵。则却因其实而命之曰伍。曰卒。曰旅。曰师而已。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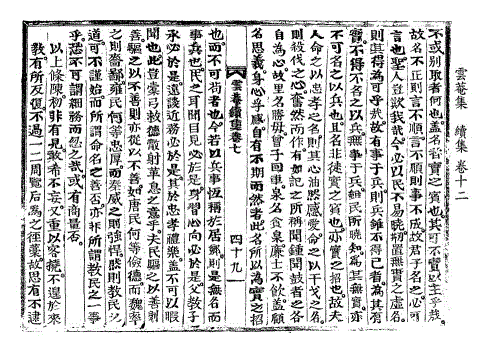 不或别取者可也。盖名者实之宾也。其可不实以主乎哉。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圣人岂欺我哉。今必以民不易晓。刱置无实之虚名。则其得为可乎哉。故有事于兵。则兵虽不得已者。为其有实。不得不名之以兵。无事于兵。虽民所晓知。为其无实。亦不可名之以兵也。且名非徒实之宾也。亦实之招也。故夫人命之以忠孝之名。则其心油然感爱。命之以干戈之名。则杀伐之心。奋然而作。有如记之所称闻钟闻鼓者之各自为心。故里名胜母。曾子回车。泉名贪泉。廉士不饮。盖顾名思义。身心孚感。自有不期而然者。此名所以为实之招也。而不可苟者也。今若以兵事恒称于居乡。则是无名而事兵也。民之耳闻目见必于是。身习心向必于是。父教子承必于是。远谈近务必于是。其于忠孝礼乐。盖不可以暇闻也。此岂橐弓救德散射革息之意乎。夫民驱之以善则善。驱之以不善则亦从以不善。如唐民何等俭德。而魏率之则啬鄙。雍民何等忠厚。而秦威之则强悍。然则教民之道。可不谨始。而所谓命名之善否。亦非所谓教民之一事乎。恐不可谓细务而忽之哉。或有商量否。
不或别取者可也。盖名者实之宾也。其可不实以主乎哉。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圣人岂欺我哉。今必以民不易晓。刱置无实之虚名。则其得为可乎哉。故有事于兵。则兵虽不得已者。为其有实。不得不名之以兵。无事于兵。虽民所晓知。为其无实。亦不可名之以兵也。且名非徒实之宾也。亦实之招也。故夫人命之以忠孝之名。则其心油然感爱。命之以干戈之名。则杀伐之心。奋然而作。有如记之所称闻钟闻鼓者之各自为心。故里名胜母。曾子回车。泉名贪泉。廉士不饮。盖顾名思义。身心孚感。自有不期而然者。此名所以为实之招也。而不可苟者也。今若以兵事恒称于居乡。则是无名而事兵也。民之耳闻目见必于是。身习心向必于是。父教子承必于是。远谈近务必于是。其于忠孝礼乐。盖不可以暇闻也。此岂橐弓救德散射革息之意乎。夫民驱之以善则善。驱之以不善则亦从以不善。如唐民何等俭德。而魏率之则啬鄙。雍民何等忠厚。而秦威之则强悍。然则教民之道。可不谨始。而所谓命名之善否。亦非所谓教民之一事乎。恐不可谓细务而忽之哉。或有商量否。以上条陈。初非有见。敢希不妄。又重以客挠。不遑于来教。有所反复。不过一二周览后为之径藁。故思有不逮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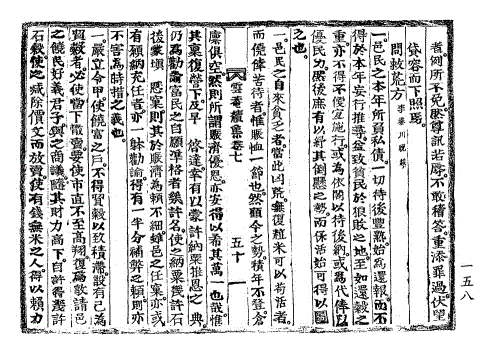 者。例所不免。然尊讯若辱。不敢稽答。重添罪过。伏望贷容而下照焉。
者。例所不免。然尊讯若辱。不敢稽答。重添罪过。伏望贷容而下照焉。[答李侯晚绥(九条)]
问救荒方(李泰川晚绥)
一。邑民之本年所负私债。一切待后丰熟。始为还报。而不得于本年妄行推寻。益致贫民于狼败之地。至如还谷之重。亦不得不便宜施行。或为依阁以待后纳。或为代俸以优民力。然后庶有以纾其倒悬之势。而保活始可得以图之也。
一。邑民之自来贫乏者。当此凶荒。无复粒米可以苟活者。而侥倖苦待者。惟赈恤一节也。然顾今之势。积年不登。仓廪俱空。然则所谓赈济优恩。亦安得以希其万一也哉。惟其禀复营下。及早 启达。幸有以蒙许纳粟推恩之 典。仍为劝谕富民之自愿准格者几许名。使之纳粟几许石后蒙填 恩窠。则其于赈济为赖不细。虽邑之任窠。亦或有愿纳充任者。亦一体劝谕。得有一半分补弊之赖。则亦不害为时措之义也。
一。严立令甲。使饶富之户。不得贸谷以致积滞。设有已为贸谷者。必使当下散卖。要使市直不至高翔。复为敦请邑之饶民好义君子。与之商议。随其财力高下。自许得几许石谷。使之减除价文而放卖。使有钱无米之人。得以赖力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9H 页
 买食。则亦为一方便也。
买食。则亦为一方便也。一。办取几许钱两。择给邑之善贾者。前去邻邑如慈顺川丰熟处。买运米谷。循还放卖。以待贫民买食。仍以窠任激赏其最有功效者几许名。则其懋迁化居之道。足以有赖焉。
一。酒饴之禁。固在所严。而此后设有解弛之虞。特复严敕。不或小有犯冒之弊。然后于民始有以蒙惠之实矣。
一。使民预择早粟之种。待春即为播种。复多植牟麦蔓菁之属。而有以助艰乏之窘也。
右件只采荒政中近似底方便。有以仰备考阅。而恐未必为合施之切务也。幸垂精察。有可采则采之。否则投诸笆篱。亦一事也。而书成后追闻民语。皆以为今次营承许代俸而归。面面相贺。欢声如雷。如得再生之秋焉。未知果否。或者果尔。则诚为快活。而亦于民所告第一条。不谓其符合之如是甚妙也。
一。将来彊借劫夺之患。恐在所难免。若不及早检敕。则蔓延弊瘼。支撑不得。然亦须先示存恤之意。然后禁其为非。则庶几人心怀德畏威。易为弹戢。此今日所以急于救荒而不敢有所慢忽之意。于此如或有右项售奸行弊之辈。则又不可不为之严切处置也。故必须预以此等辞意
云庵续集卷之十二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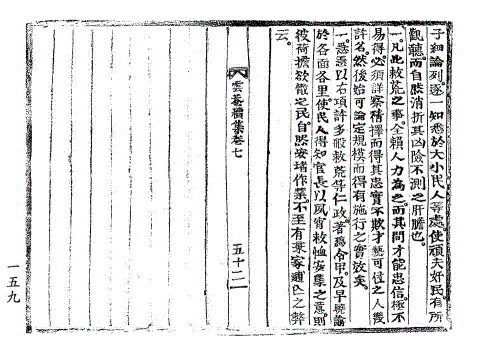 子细论列。逐一知悉于大小民人等处。使顽夫奸民。有所观听。而自然消折其凶险不测之肝胆也。
子细论列。逐一知悉于大小民人等处。使顽夫奸民。有所观听。而自然消折其凶险不测之肝胆也。一。凡此救荒之事。全赖人力为之。而其间才能忠信。极不易得。必须详察精择而得其忠实不欺才艺可仗之人几许名。然后始可论定规模而得有施行之实效矣。
一。急急以右项许多般救荒等仁政。著为令甲。及早晓谕于各面各里。使民人得知官长以夙宵救恤安集之意。则彼荷担欲散之民。自然安堵作业。不至有弃家逋亡之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