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问目
问目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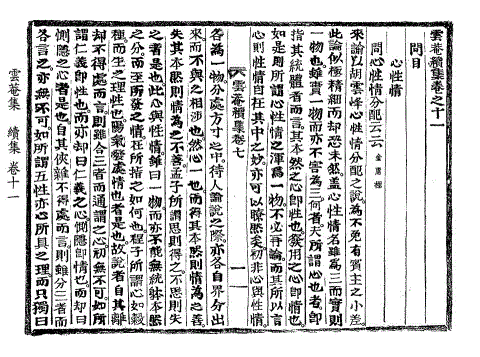 心性情
心性情[答金庸极]
问心性情分配云云(金庸极)
来谕以胡云峰心性情分配之说。为不免有宾主之小差。此论似极精细而却恐未然。盖心性情名虽为三而实则一物也。虽实一物而亦不害为三。何者。夫所谓心也者。即指其统体者而言。其本然之心即性也。发用之心即情也。如是则所谓心性情之浑为一物。不必再论。而其所以言心则性情自在其中之妙。亦可以瞭然矣。初非心与性情。各为一物。分处方寸之中。待人论说之际。亦各自界分出来。而不与之相涉也。然心一也。而得其本然则情为之善。失其本然则情为之不善。孟子所谓思则得之。不思则失之者是也。此心与性情。虽曰一物。而亦不能无统体本然之分。而至所发之情。在所指之如何也。程子所谓心如谷种。而生之理性也。阳气发处情也者是也。故说者自其离却不得处而言。则虽合三者而通谓之心。初无不可。如所谓仁义即性也。而亦却曰仁义之心。恻隐即情也。而却曰恻隐之心者是也。自其侠杂不得处而言。则虽分三者而各言之。亦无不可。如所谓五性亦心所具之理。而只独曰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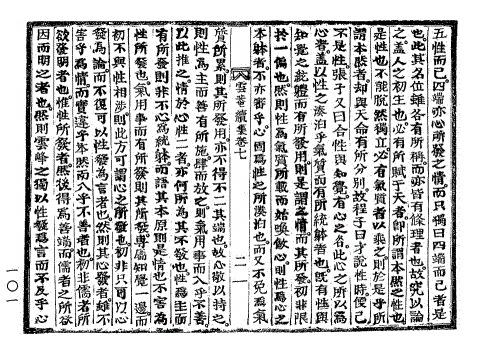 五性而已。四端亦心所发之情。而只独曰四端而已者是也。此其名位虽各有所称。而亦皆有条理者也。故究以论之。盖人之初生也。必有所赋于天者。即所谓本然之性也。是性也不能脱然独立。必有气质者以乘之。则于是乎所谓本然者。却与天命有所分别。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张子又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心之所以为心者。盖以性之凑泊乎气质而有所统体者也。既有性与知觉之统体而有所发用。则是谓之情。而其所发。初非限于一偏也。然则性为气质所载而始唤做心。则性为心之本体者。不亦审乎。心固为性之所凑泊也。而又不免为气质所累。则其所发用。亦不得不二其端也。故心敬以持之。则性为主而善有所施。肆而放之。则气用事而入乎不善。以此推之。情于心性二者。亦何所为其不发也。性为主而有所发则非不心为统体。而语其本原则是情也不害为性所发也。气用事而有所发则其所发。专属知觉一边。而初不与性相涉。则此方可谓心之所发也。初非只可以心发为论。而不复可以性发为言者也。然则其心发者。虽不害乎为情。而实违乎本然而入乎不善者也。初非儒者所欲发明者也。惟性所发者。然后得为善端。而儒者之所欲因而明之者也。然则云峰之独以性发为言而不及乎心
五性而已。四端亦心所发之情。而只独曰四端而已者是也。此其名位虽各有所称。而亦皆有条理者也。故究以论之。盖人之初生也。必有所赋于天者。即所谓本然之性也。是性也不能脱然独立。必有气质者以乘之。则于是乎所谓本然者。却与天命有所分别。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张子又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心之所以为心者。盖以性之凑泊乎气质而有所统体者也。既有性与知觉之统体而有所发用。则是谓之情。而其所发。初非限于一偏也。然则性为气质所载而始唤做心。则性为心之本体者。不亦审乎。心固为性之所凑泊也。而又不免为气质所累。则其所发用。亦不得不二其端也。故心敬以持之。则性为主而善有所施。肆而放之。则气用事而入乎不善。以此推之。情于心性二者。亦何所为其不发也。性为主而有所发则非不心为统体。而语其本原则是情也不害为性所发也。气用事而有所发则其所发。专属知觉一边。而初不与性相涉。则此方可谓心之所发也。初非只可以心发为论。而不复可以性发为言者也。然则其心发者。虽不害乎为情。而实违乎本然而入乎不善者也。初非儒者所欲发明者也。惟性所发者。然后得为善端。而儒者之所欲因而明之者也。然则云峰之独以性发为言而不及乎心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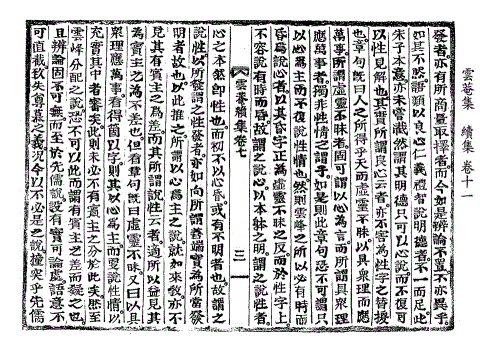 发者。亦有所商量取择者。而今如是辨论不置。不亦异乎。如其不然。语类以良心仁义礼智说明德者。不一而足。此朱子本意。亦未尝截然谓其明德只可以心说。而不复可以性见解也。其实所谓良心云者。亦不害为性字之替换也。章句既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所谓虚灵不昧者。固可谓以心为言。而所谓具众理应万事者。独非性情之谓乎。如是则此章句恐不可谓只以心为主而不复说性情也。然则云峰之所以必有时而昏为说心者。以其昏字正为虚灵不昧之反。而于性字上。不容说有时而昏。故谓之说心。以本体之明。谓之说性者。心之本然即性也。而初不以心昏。或有不明者也。故谓之说性。以所发谓之性发者。亦如向所谓善端实为所当发明者故也。以此推之。所谓以心为主之说。就如来教。亦不见其有宾主之为差。而其所谓说性云者。适所以益见其为宾主之为不差也。但看章句既曰虚灵不昧。又曰以具众理应万事。看得个以字。则其以心为主。而更说性情。以充实其中者审矣。此则未必不有宾主之分于此矣。然至云峰分配之说。恐不可以此而谓有宾主之差而疑之也。且辨论固不可无。而至于先儒说。设有实可论处。语意不可直截。致失尊慕之义。况今以不必是之说。撞突乎先儒
发者。亦有所商量取择者。而今如是辨论不置。不亦异乎。如其不然。语类以良心仁义礼智说明德者。不一而足。此朱子本意。亦未尝截然谓其明德只可以心说。而不复可以性见解也。其实所谓良心云者。亦不害为性字之替换也。章句既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所谓虚灵不昧者。固可谓以心为言。而所谓具众理应万事者。独非性情之谓乎。如是则此章句恐不可谓只以心为主而不复说性情也。然则云峰之所以必有时而昏为说心者。以其昏字正为虚灵不昧之反。而于性字上。不容说有时而昏。故谓之说心。以本体之明。谓之说性者。心之本然即性也。而初不以心昏。或有不明者也。故谓之说性。以所发谓之性发者。亦如向所谓善端实为所当发明者故也。以此推之。所谓以心为主之说。就如来教。亦不见其有宾主之为差。而其所谓说性云者。适所以益见其为宾主之为不差也。但看章句既曰虚灵不昧。又曰以具众理应万事。看得个以字。则其以心为主。而更说性情。以充实其中者审矣。此则未必不有宾主之分于此矣。然至云峰分配之说。恐不可以此而谓有宾主之差而疑之也。且辨论固不可无。而至于先儒说。设有实可论处。语意不可直截。致失尊慕之义。况今以不必是之说。撞突乎先儒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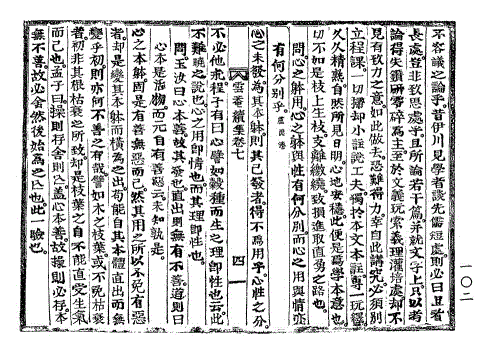 不容议之论乎。昔伊川见学者谈先儒短处。则必曰且看长处。岂非致思处乎。且所论若干篇。并就文字上。只以考论得失钻研零碎为主。至于文义玩索义理灌培处。却不见有致力之意。如此做去。恐难得力。幸自此讲究。必须别立程课。一切扫却小注说工夫。独于本文本注。专一玩绎。久久精熟。自然所见日明。心地安稳。此便是为学本意也。切不如是枝上生枝。支离缴绕。致损进取直勇之路也。
不容议之论乎。昔伊川见学者谈先儒短处。则必曰且看长处。岂非致思处乎。且所论若干篇。并就文字上。只以考论得失钻研零碎为主。至于文义玩索义理灌培处。却不见有致力之意。如此做去。恐难得力。幸自此讲究。必须别立程课。一切扫却小注说工夫。独于本文本注。专一玩绎。久久精熟。自然所见日明。心地安稳。此便是为学本意也。切不如是枝上生枝。支离缴绕。致损进取直勇之路也。[答卢德济(二条)]
问。心之体用。心之体与性有何分别。而心之用与情亦有何分别乎。(卢德济)
心之未发。为其本体。则其已发者。得不为用乎。心性之分。不必他求。程子有曰心譬如谷种而生之理既性也云。此不难晓之说也。心之用即情也。而其理既性也。
问。玉汝曰心本善。故其发也。直出则无有不善。道则曰心本是活物。而元自有善恶云。未知孰是。
心之本体。固是有善无恶而已。然其用之所以不免有恶者。却是变其本体而横为之出。苟能自其本体直出而无变乎初。则亦何不善之有哉。譬如木之枝叶。或不免枯衰者。初非其根枯衰之所致。却是枝叶之自不能直受生气而已也。孟子曰。操则存舍则亡。盖心本善。故操则必存。本无不善。故必舍然后始为之亡也。此一验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3H 页
 [答朴世和(二条)]
[答朴世和(二条)]问。仁义礼智信是性。孝亲忠君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者是情。使其具足者是心。(朴世和)
此论固好。但于义理界分。觉未精细。盖仁义礼智。固是为性。而其恻隐羞恶。即性之发为情者也。其忠孝。即情之见为行事者也。此盖各随地头而其脉络名位。有不可毫发混杂者。若以恻隐孝弟俱属于情。则不惟界分混错。亦无以见义理次第一贯之妙也。且性情固不出乎心体之外。而不为子细说破。则亦是鹘突。不为实见也。盖性只是理。情只是发见也。而心则乃所以具此理而行此发见者也耳。
问。寂然不动。是心之体。是虚灵。感而遂通。是心之用。是知觉。其体用之妙者。是神明。就此正好看性情。
寂然不动。即性也。固可谓心之体也。而谓之虚灵则不可。盖性以理言。而虚灵则兼理气之谓也。感而遂通。固似知觉之谓也。而一则所以说性发为情之妙。一则专以气质为言者也。其所主而为言者。亦大有所径庭焉。所谓体用之妙。妙字不知是说心之功用否。果尔则恐不若以主宰二字易之。未知如何。所谓就此正好看性情云者。亦不知是指上文心之体心之用而言邪。若果如是则煞有可疑。盖虚灵知觉。岂可以性情为论邪。窃看论说。类多看得道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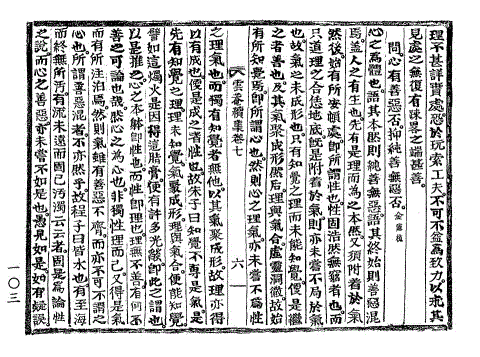 理不甚详实处。恐于玩索工夫。不可不益为致力。以求其见处之无复有疏略之端甚善。
理不甚详实处。恐于玩索工夫。不可不益为致力。以求其见处之无复有疏略之端甚善。[答金宪植]
问。心有善恶否。抑纯善无恶否。(金宪植)
心之为体也。语其本然则纯善无恶。语其终始则善恶混焉。盖人之有生也。先有是理而为之本然。又须附着于气然后。始有所安顿处。即所谓性也。性固浩然无穷者也。而只道理之合恁地底。既是附着于气。则亦未尝不局于气也。故气之未成形也。只有知觉之理而未能知觉。便是继之者善也。及其气聚成形然后。理与气合。虚灵洞彻。故始有所知觉焉。即所谓心也。然则心之理气。亦未尝不为性之理气也。而独有知觉者无他。以其气聚成形。故理亦得以有成也。便是成之者性也。故朱子曰知觉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燄。即此之谓也。以是推之。心之本体即性也。而性即理也。理无不善。有何不善之可论也哉。然心之为心也。非独性理而已。又得是气而有所注泊焉。然则气虽有善恶不齐。而亦不可不谓之心也。所谓善恶混者。不亦然乎。故程子曰皆水也。有至海而终无所污。有流未远而固已污浊云云者。固是为论性之说。而心之善恶。亦未尝不如是也。愚见如是。如有疑误。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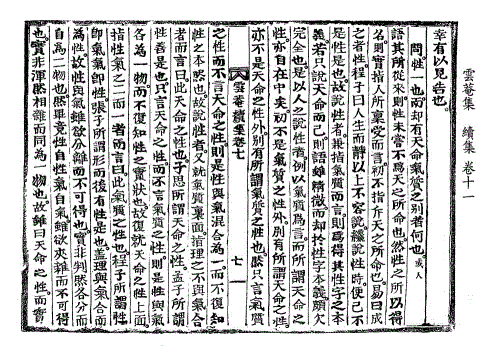 幸有以见告也。
幸有以见告也。[答或人]
问。性一也。而却有天命气质之别者何也。(或人)
语其所从来。则性未尝不为天之所命也。然性之所以得名。则实指人所禀受而言。初不指斥天之所命也。易曰成之者性。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是也。故说性者。兼指气质而言。则为得其性字之本义。若只说天命而已。则语虽精微。而却于性字本义。颇欠完全也。是以人之说性者。例以气质为言。而所谓天命之性。亦自在中矣。初不是气质之性外。别有所谓天命之性。亦不是天命之性外。别有所谓气质之性也。然只言气质之性而不言天命之性。则是性与气混合为一。而不复知性之本然也。故说性者。又就气质里面。指理之不与气合者而言曰。此天命之性也。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是也。只言天命之性。而不言气质之性。则是性与气各为一物。而不复知性之实状也。故复就天命之性上面。指性气之二而一者而言曰。此气质之性也。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形而后有性是也。盖理与气合而为性。故性与气虽欲分离而不可得也。实非判然各分而自为二物也。然毕竟性自性气自气。虽欲夹杂而不可得也。实非浑然相杂而同为一物也。故虽曰天命之性。而实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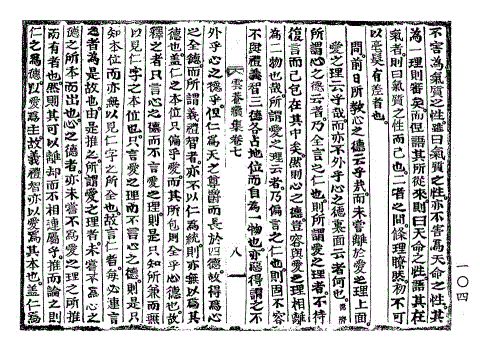 不害为气质之性。虽曰气质之性。亦不害为天命之性。其为一理则审矣。而但语其所从来。则曰天命之性。语其在气者。则曰气质之性而已也。二者之间。条理瞭然。初不可以毫发有差者也。
不害为气质之性。虽曰气质之性。亦不害为天命之性。其为一理则审矣。而但语其所从来。则曰天命之性。语其在气者。则曰气质之性而已也。二者之间。条理瞭然。初不可以毫发有差者也。[答卢德济]
问。前日所教心之德云乎哉。而未尝离于爱之理上面。爱之理云乎哉。而亦不外乎心之德里面云者何也。(德济)
所谓心之德云者。乃全言之仁也。则所谓爱之理者。不待复言而已包在其中矣。然则心之德。岂容与爱之理相离为二物也哉。所谓爱之理云者。乃偏言之仁也。则固不容不与礼义智三德各占地位而自为一物也。亦恶得谓之不外乎心之德乎。但仁为天之尊爵而长于四德。故得为心之全德。而所谓义礼智者。亦不以仁为统。则亦无以为其德也。盖仁之本位只偏乎爱。而其所包则全乎心德也。故释之者只言心之德而不言爱之理。则是只知所兼而无以见仁字之本位也。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则是只知本位而亦无以见仁字之所全也。故言仁者。每必连言之者为是故也。由是推之。所谓爱之理者。未尝不为心之德之所本而出也。心之德者。亦未尝不为爱之理之所推而有者也。然则其可以离却而不相连属乎。推而论之则仁之为德。以爱为主。故义礼智亦以爱为其本也。盖仁为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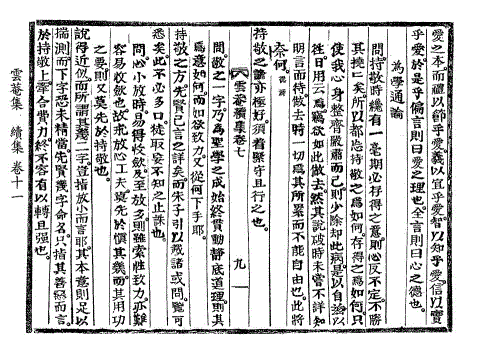 爱之本。而礼以节乎爱。义以宜乎爱。智以知乎爱。信以实乎爱。于是乎偏言则曰爱之理也。全言则曰心之德也。
爱之本。而礼以节乎爱。义以宜乎爱。智以知乎爱。信以实乎爱。于是乎偏言则曰爱之理也。全言则曰心之德也。为学通论
[答卢德济(五条)]
问。持敬时才有一毫期必存得之意。则心反不定。不胜其挠挠矣。所以都忘持敬之为如何。存得之为如何。只使我心身整齐严肃而已。则少除却此病。是以自玆以往。日用云为。窃欲如此做去。然其说破时未尝不详知明言而待。做去时一切为其所累而不能自由也。此将奈何。(德济)
持敬之论亦极好。须着紧守且行之也。
问。敬之一字。乃为圣学之成始终贯动静底道理。则其为意如何。而如欲致力。又从何下手耶。
持敬之方。先贤已言之详矣。而朱子引以载诸或问。览可悉矣。此不必多口。徒取妄不知之止诛也。
问。心小放时。易得收敛。及至放多。则虽索性致力。亦难容易收敛也。故求放心工夫。莫先于慎其几。而其用功之要。则又莫先于持敬也。
说得近似。而所谓其几二字。岂指放小而言耶。其本意则足以揣测。而下字恐未精当。先贤几字命名。只指其善恶而言。于持敬上。牵合费力。终不容有以转且强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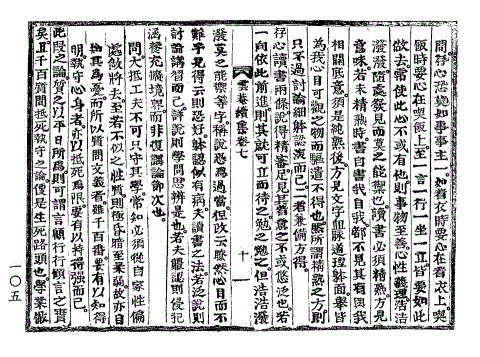 问。存心恐莫如事事主一。如着衣时要心在着衣上。吃饭时要心在吃饭上。至一言一行一坐一立。皆要如此做去。常使此心不或有他。则事物至善。心性义理。浩浩泼泼。随处发见而莫之能御也。读书必须精熟。方见意味。若未精熟时。书自书我自我。都不见其有与我相关底意。须是纯熟后。方见文字血脉道理体面。举皆为我心目可观之物而驱遣不得也。然所谓精熟之方。则只不过讨论细体认深而已。二者兼备方得。
问。存心恐莫如事事主一。如着衣时要心在着衣上。吃饭时要心在吃饭上。至一言一行一坐一立。皆要如此做去。常使此心不或有他。则事物至善。心性义理。浩浩泼泼。随处发见而莫之能御也。读书必须精熟。方见意味。若未精熟时。书自书我自我。都不见其有与我相关底意。须是纯熟后。方见文字血脉道理体面。举皆为我心目可观之物而驱遣不得也。然所谓精熟之方。则只不过讨论细体认深而已。二者兼备方得。存心读书两条。说得精审。足见其着意之不或悠泛也。若一向依此前进。则其就可立而待之。勉之勉之。但浩浩泼泼莫之能御等字。称说恐为过当。但改云瞭然心目而不难乎见得云则恐好。体认似有病。夫读书之法。若泛说则讨论讲习而已。详说则学问思辨是也。若夫体认则侵犯涵养充扩境界。而非复讲论节次也。
问。大抵工夫不可只守其学。常知必须从自家性偏处做将去。至若不似之性质。则极昏暗至柔弱。故亦自知其为忧。而所以质问文义者。虽千百番。要有以知得明。执守心身者。亦以抵死为限。要有以持得强而已。
此段之论。质之以平日所为。则可谓言顾行行顾言之实矣。且千百质问抵死执守之论。便是生死路头也。学业做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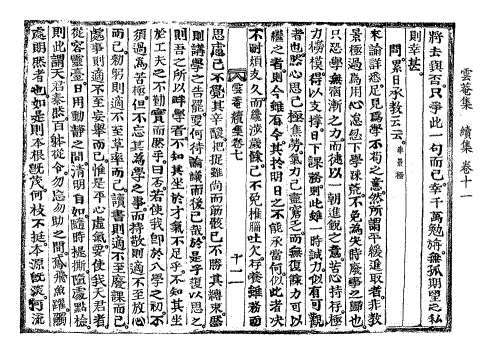 将去与否。只争此一句而已。幸千万勉旃。无孤期望之私则幸甚。
将去与否。只争此一句而已。幸千万勉旃。无孤期望之私则幸甚。[答车景极]
问。累日承教云云。(车景极)
来谕详悉。足见为学不苟之意。然所谓平缓进取者。非教景极过为用心怠忽下学疏荒。不免为失时废事之归也。只恐学无宿渐之力。而徒以一朝进锐之意。苦心持存。极力捞模。得以支撑。日下课务。则此虽一时诚力。似有可观者也。然心思已极焦劳。气力已尽窘乏。而无复馀力可以继之者。则今虽有今。其于明日之不能承当何。似此者决不耐烦支久。而才涉岁馀。已不免椎脑吐欠。存养虽务而思虑已不觉其辛酸。把捉虽尚而筋骸已不胜其缚束。然则讲学之告罢。更何待论议而后已哉。于是乎复以思之。则吾之所以畔学者。不知其坐于才气不足乎。不知其坐于工夫之不勤实而然乎。曰否。若使我即于入学之初。不须过为苦极。但不忘其为学之事。而持敬则适不至放心而已。敕躬则适不至草率而已。读书则适不至废课而已。处事则适不至妄举而已。惟是平心虚气。要使我天君者。从容灵台。日用动静之间。清明自如。随时提撕。随处点检。则此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勿忘勿助之间。鸢飞鱼跃。触处朗然者也。如是则本根既茂。何枝不挺。本源既深。何流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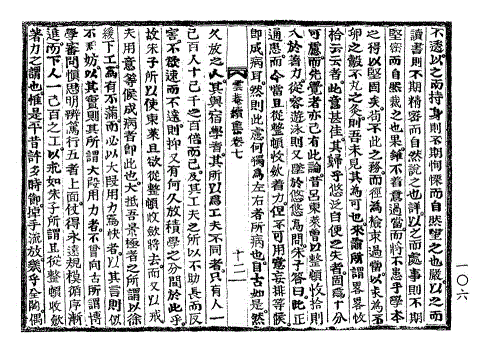 不透。以之而持身则不期恂慄而自然望之也严。以之而读书则不期精密而自然说之也详。以之而处事则不期坚密而自然裁之也果。虽不着意过当。而将不患乎学本之得以坚固矣。苟不此之务。而径为检束过当。以求为不卵之鷇不丸之灸。则吾未见其为可也。来谕所谓略略收拾云云者。此意甚佳。其归乎悠泛自便之失者。固为十分可虑。而先觉者亦已有此论。昔吕东莱曾以整顿收拾则入于著力。从容游泳则又坠于悠悠为问。朱子答曰。此正通患。而今当且从整顿收敛着力。但不可用意妄排等候。即成病耳。然则此虑何独为左右者所病也。自古如是。然久放之人。其与宿学者。其所以为工夫不同者。只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百倍而已。及其工夫之所以不助长而反害。不欲速而不达。则抑又有何久放积学之分间于此乎。故朱子所以使东莱且欲从整顿收敛将去。而又以戒夫用意等候成病者即此也。大抵吾景极者之所谓以徐缓下工。为有不满。而必以大段用力为快者。以其言则似不为妨。以其实则其所谓大段用力者。不曾向古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上面。仗得永远规模循序渐进。而下人一己百之工。以求如朱子所谓且从整顿收敛著力之谓也。惟是平昔许多时节。掉手流放。几乎全阁。偶
不透。以之而持身则不期恂慄而自然望之也严。以之而读书则不期精密而自然说之也详。以之而处事则不期坚密而自然裁之也果。虽不着意过当。而将不患乎学本之得以坚固矣。苟不此之务。而径为检束过当。以求为不卵之鷇不丸之灸。则吾未见其为可也。来谕所谓略略收拾云云者。此意甚佳。其归乎悠泛自便之失者。固为十分可虑。而先觉者亦已有此论。昔吕东莱曾以整顿收拾则入于著力。从容游泳则又坠于悠悠为问。朱子答曰。此正通患。而今当且从整顿收敛着力。但不可用意妄排等候。即成病耳。然则此虑何独为左右者所病也。自古如是。然久放之人。其与宿学者。其所以为工夫不同者。只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百倍而已。及其工夫之所以不助长而反害。不欲速而不达。则抑又有何久放积学之分间于此乎。故朱子所以使东莱且欲从整顿收敛将去。而又以戒夫用意等候成病者即此也。大抵吾景极者之所谓以徐缓下工。为有不满。而必以大段用力为快者。以其言则似不为妨。以其实则其所谓大段用力者。不曾向古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上面。仗得永远规模循序渐进。而下人一己百之工。以求如朱子所谓且从整顿收敛著力之谓也。惟是平昔许多时节。掉手流放。几乎全阁。偶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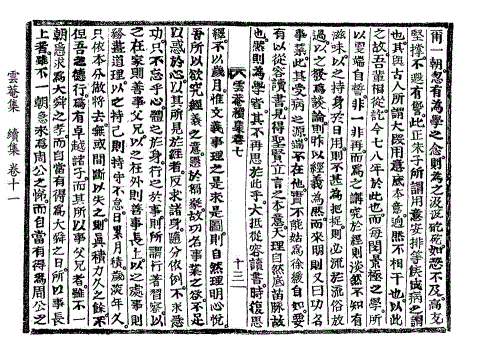 尔一朝。忽有为学之念。则为之汲汲矻矻。如恐不及。高支坚撑。不遐有愆。此正朱子所谓用意安排等候成病之谓也。其与古人所谓大段用意底本意。迥然不相干也。以此之故。吾辈相从。讫今七八年于此也。而每闵景极之学。所以更端自誓。非一非再。而为之讲究于经则淡然不知有滋味。以之持身于日用。则不甚为把捉。则必流于流俗放过。以之发为谈论。则昨以经义为然。而来明则又曰功名事业。此其受病之源。端不在他。实不能姑为徐缓自如。要有以从容读书。见得圣贤立言之本意。天理自然底苗脉故也。然则为学者。其不再思于此乎。大抵从容读书。时复思绎。不以岁月。惟文义事理之是求是图。则自然理明心悦。吾所以欲究经义之意。急于刍豢。故功名事业之欲。不足以惑于心。以其所见于经者。反求诸身。随分依例。不求急功。只不忘乎心。体之于身。行之于事。则所谓行著习察。以之在家则善事父兄。以之在外则善事长上。以之处事则务尽道理。以之持己则持守不怠。日累月积。岁深年久。只依本分做将去。无或间断以失之。则真积力久之馀。不但吾之德行。为有卓越诸子。而其所以事父兄者。虽不一朝急求为大舜之孝。而自当有得为大舜之日。所以事长上者。虽不一朝急求为周公之悌。而自当有得为周公之
尔一朝。忽有为学之念。则为之汲汲矻矻。如恐不及。高支坚撑。不遐有愆。此正朱子所谓用意安排等候成病之谓也。其与古人所谓大段用意底本意。迥然不相干也。以此之故。吾辈相从。讫今七八年于此也。而每闵景极之学。所以更端自誓。非一非再。而为之讲究于经则淡然不知有滋味。以之持身于日用。则不甚为把捉。则必流于流俗放过。以之发为谈论。则昨以经义为然。而来明则又曰功名事业。此其受病之源。端不在他。实不能姑为徐缓自如。要有以从容读书。见得圣贤立言之本意。天理自然底苗脉故也。然则为学者。其不再思于此乎。大抵从容读书。时复思绎。不以岁月。惟文义事理之是求是图。则自然理明心悦。吾所以欲究经义之意。急于刍豢。故功名事业之欲。不足以惑于心。以其所见于经者。反求诸身。随分依例。不求急功。只不忘乎心。体之于身。行之于事。则所谓行著习察。以之在家则善事父兄。以之在外则善事长上。以之处事则务尽道理。以之持己则持守不怠。日累月积。岁深年久。只依本分做将去。无或间断以失之。则真积力久之馀。不但吾之德行。为有卓越诸子。而其所以事父兄者。虽不一朝急求为大舜之孝。而自当有得为大舜之日。所以事长上者。虽不一朝急求为周公之悌。而自当有得为周公之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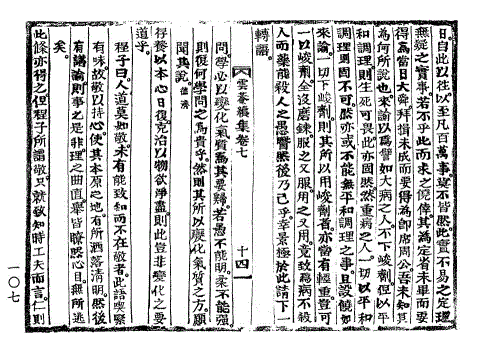 日。自此以往。以至凡百万事。莫不皆然。此实不易之定理。无疑之实事。若不乎此而求之侥倖。其为定省未毕而要得为当日大舜。拜揖未成而要得为即席周公。吾未知其为何所说也。来谕以为譬如大病之人。不下峻剂。但以平和调理。则生死可畏。此亦固然。然重病之人。一切以平和调理则固不可。然亦或不能无平和调理之事。且设饶如来谕。一切下峻剂。则其所以用峻剂者。亦当有轻重。岂可一以峻剂。全没磨鍊。服之又服。用之又用。竟致为病不杀人而药能杀人之愚医然后乃已乎。幸景极于此请下一转语。
日。自此以往。以至凡百万事。莫不皆然。此实不易之定理。无疑之实事。若不乎此而求之侥倖。其为定省未毕而要得为当日大舜。拜揖未成而要得为即席周公。吾未知其为何所说也。来谕以为譬如大病之人。不下峻剂。但以平和调理。则生死可畏。此亦固然。然重病之人。一切以平和调理则固不可。然亦或不能无平和调理之事。且设饶如来谕。一切下峻剂。则其所以用峻剂者。亦当有轻重。岂可一以峻剂。全没磨鍊。服之又服。用之又用。竟致为病不杀人而药能杀人之愚医然后乃已乎。幸景极于此请下一转语。[答卢德济(二条)]
问。学必以变化气质为其要归。若愚不能明。柔不能强。则复何学问之为贵乎。然则其所以变化气质之方。愿闻其说。(德济)
存养以本心日复。克治以物欲净尽。则此岂非变化之要道乎。
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语吃紧有味。故敬以持心。使其本原之地。有所洒落清明。然后有讲论。则事之是非。理之曲直。举皆瞭然心目。无所逃矣。
此条亦得之。但程子所谓敬。只就致知时工夫而言。仁则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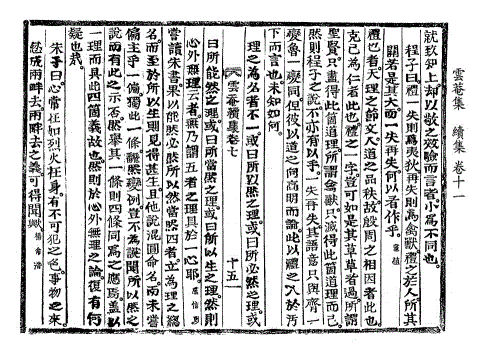 就致知上。却以敬之效验而言者。小为不同也。
就致知上。却以敬之效验而言者。小为不同也。[答金宪植]
程子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礼之于人。所其关若是其大。而一失再失。何以看作乎。(宪植)
礼也者。天理之节文。人道之品秩。故殷周之相因者此也。克己为仁者此也。礼之一字。岂可如是其草草看过。所谓圣贤。只尽得此个道理。所谓禽兽。只灭得此个道理而已。然则程子之说。不亦有以乎。一失再失。其语意只与齐一变鲁一变同。但彼以道之向高明而论。此以礼之入于污下而言也。未知如何。
[答卢信则]
理之为名者不一。或曰所以然之理。或曰所必然之理。或曰所能然之理。或曰所当然之理。或曰所以生之理。然则心外无理云者。无乃谓五者之理具于一心耶。(卢信则)
尝读朱书。果以能然必然所以然当然四者。立为理之总名。而至于所以生则见得甚生。且他说混圆命名。而未尝偏主乎一偏。独此一条。翻然变例。岂不为误闻所以然之说而有此之示否。然举其一条则四条同为之应焉。盖以一理而具此四个义故也。然则于心外无理之论。复有何疑也哉。
[答杨命浩]
朱子曰。心常在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来。忽成两畔去。两畔去之义。可得闻欤。(杨命浩)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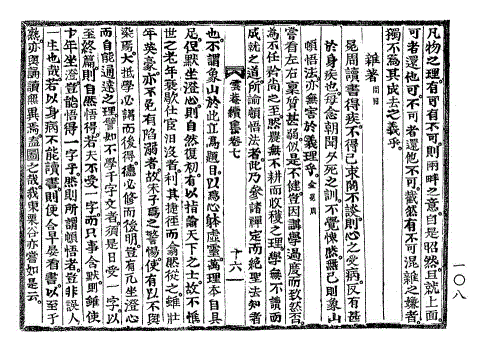 凡物之理。有可有不可。则两畔之意。自是昭然。且就上面。可者还他可。不可者还他不可。截然有不可混杂之嫌者。独不为其成去之义乎。
凡物之理。有可有不可。则两畔之意。自是昭然。且就上面。可者还他可。不可者还他不可。截然有不可混杂之嫌者。独不为其成去之义乎。杂著
[答金冕周]
冕周读书得疾。不得已束阁不谈。则心之受病。反有甚于身疾也。每念朝闻夕死之训。不觉悚然。无已则象山顿悟法。亦无害于义理乎。(金冕周)
尝看左右禀质甚弱。似是不健。岂因讲学过度而致然否。为不任矜尚之至。然农无不耕而收穫之理。学无不读而成就之道。所谕顿悟法者。此乃参诸禅定而绝圣去知者也。不谓象山于此立为题目。以为心体虚灵。万理本自具足。但默坐澄心。则自然复初。有以指谕天下之士。故不惟世之老年衰歇仕宦汩没者。利其捷径而翕然从之。虽壮年英豪。亦不免有陷溺者。故朱子为之警惕。使有以不与染焉。大抵学必讲而后得。德必修而后明。岂有兀坐澄心而自能通达之理。譬如不学千字文者。须是日受一字。以至终篇。则自然悟得。若夫不受一字。而只事含默。则虽使十年坐澄。岂能悟得一字乎。然则所谓顿悟者。岂非误人一生也哉。若以身病不能读书。则便合早晏看书。以至于熟。亦与诵读无异焉。盍图之哉。我东栗谷亦尝如是云。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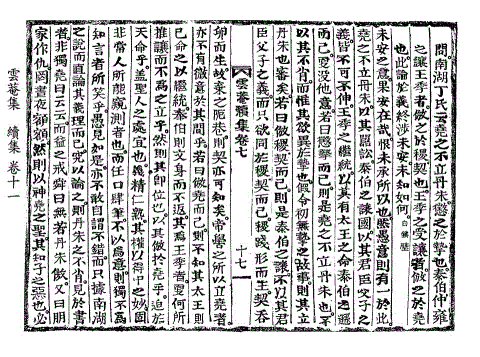 [答白镇璧]
[答白镇璧]问。南湖丁氏云尧之不立丹朱。惩之于挚也。泰伯,仲雍之让王季者。仿之于稷,契也。王季之受让者。仿之于尧也。此论于义终涉未安。未知如何。(白镇璧)
未安之意。果安在哉。恨未承所以也。然愚意则有一于此。尧之不立丹朱。以其嚚讼。泰伯之让国。以其君臣父子之义。皆不可不伸。王季之继统。以其有太王之命泰伯之逊而已。更没他意。若曰惩挚而已。则是尧之不立丹朱也。不以其不肖。而惟其欲异于挚也。假令初无挚之故事。则其立丹朱也审矣。若曰仿稷,契而已。则是泰伯之让。不以其君臣父子之义。而只欲同于稷,契而已。稷践形而生。契吞卵而生。故弃之阨巷。则契亦可知矣。帝喾之所以立尧者。亦不有微意于其间乎。若曰仿尧而已。则不知其太王则已命之以继统。泰伯则文身而不返。其为王季者。更何所推让而不为之立乎。然则其即位也。以其仿于尧乎。迫于天命乎。盖圣人之处宜也。义精仁熟。其权以得中之妙。固非常人所能窥测者也。而任口肆笔。不以为意。则独不为知言者所笑乎。愚见如是。亦不敢自谓不错。而只据南湖之说而直论其义理而已。究以论之。则丹朱之不肖。见于书者。非独尧曰云云。而益之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又曰朋家作仇。罔昼夜额额。然则以神尧之圣。其知子之恶也。必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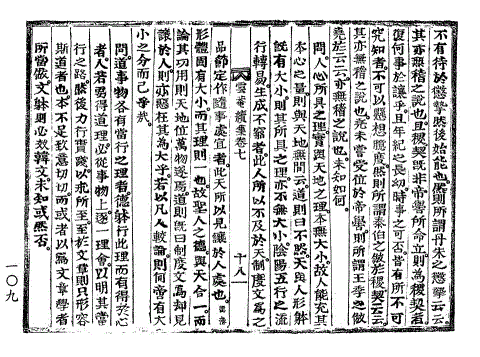 不有待于惩挚然后始能也。然则所谓丹朱之惩挚云云。其亦无稽之说也。且稷,契既非帝喾所命立。则为稷契者。复何事于让乎。且年纪之长幼。时事之可否。皆有所不可究知者。不可以悬想臆度。然则所谓泰伯之仿于稷,契云云。其亦无稽之说也。尧未尝受位于帝喾。则所谓王季之仿尧于云云。亦无稽之说也。未知如何。
不有待于惩挚然后始能也。然则所谓丹朱之惩挚云云。其亦无稽之说也。且稷,契既非帝喾所命立。则为稷契者。复何事于让乎。且年纪之长幼。时事之可否。皆有所不可究知者。不可以悬想臆度。然则所谓泰伯之仿于稷,契云云。其亦无稽之说也。尧未尝受位于帝喾。则所谓王季之仿尧于云云。亦无稽之说也。未知如何。[答卢德济(二条)]
问。人心所具之理。实与天地之理。本无大小。故人能充其本心之量。则与天地无间云。道则曰不然。天与人形体既有大小。则其所具之理。亦不无大小。阴阳五行之流行转易。生成不穷者。此人所以不及于天。制度文为之品节定作随事处宜者。此天所以见让于人处也。(德济)
形体固有大小。而其理则一也。故圣人之德。与天合一。而论其功用则天地位万物遂焉。道则既曰制度文为却见让于人。则亦恶在其为大乎。若以凡人较论。则何啻有大小之分而已乎哉。
问。道事物各有当行之理者。德体行此理而有得于心者。人若要得道理。必从事物上。逐一理会。以明其当行之路。然后力行实践。以求所至。至于文章则只形容斯道者也。本不足致意切切。而或者以为文章学者所当做。文体则必效韩文。未知或然否。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0H 页
 道德二字。如是看得固为好。然也有如此看过处。亦有不如此看过处。如率性之谓道道字。却是指其体得而言。明德德字。又指得于天者而言。史所谓德光之德字。又别是一说也。此等要当循其地头而各自体认出来。方为周遍无空阙不到之弊也。示谕作文之弊。诚如云云。而所谓作文当法韩文者。未知为谁。吾欲谛看其面也。且文体之论。固不为急。而亦自有词翰儒家体格不容混合而说也。为儒者若欲作文。则固当以儒为尚。况韩文其体格自别。又为词翰家之酋长也。设使学得。便是自为一格也。若或如人说则我东栗尤诸先达。固不以文体全不致意。而却未尝以韩文为法者。岂无所见而然耶。此说甚长。非面不既也。
道德二字。如是看得固为好。然也有如此看过处。亦有不如此看过处。如率性之谓道道字。却是指其体得而言。明德德字。又指得于天者而言。史所谓德光之德字。又别是一说也。此等要当循其地头而各自体认出来。方为周遍无空阙不到之弊也。示谕作文之弊。诚如云云。而所谓作文当法韩文者。未知为谁。吾欲谛看其面也。且文体之论。固不为急。而亦自有词翰儒家体格不容混合而说也。为儒者若欲作文。则固当以儒为尚。况韩文其体格自别。又为词翰家之酋长也。设使学得。便是自为一格也。若或如人说则我东栗尤诸先达。固不以文体全不致意。而却未尝以韩文为法者。岂无所见而然耶。此说甚长。非面不既也。[答金秉熙]
窃闻湖洛诸儒之辨条件有三。人物性曰同曰异。心体曰本善曰有善恶。明德曰有分数曰无分数云云。(金秉熙)
所示三条。此为大是非处。第当惕然高跽以俟论定而已。岂妄容喙。自求为不知其量之流乎。又况委巷孤陋。本不知谁为湖谁为洛乎。姑依来示。略有所条。请幸有以斤正之也。自天赋之初而论之。则人物同禀五常之性而无有异同。譬则雨下沛然。而江河鼎钟。一是充满。有何不均之可论也哉。然自其人禀之后而论之。则人物之性。局于气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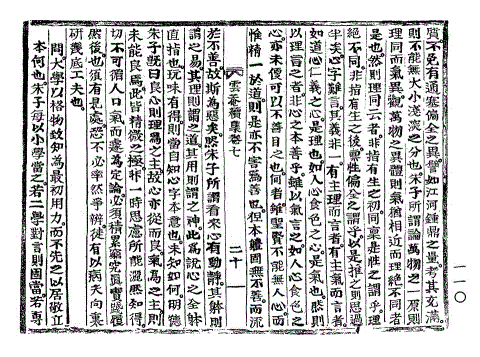 质。不免有通塞偏全之异。譬如江河钟鼎之量。考其充满。则不能无大小浅深之分也。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是也。然则理同云者。非指有生之初。同禀是性之谓乎。理绝不同。非指有生之后。禀性偏全之谓乎。以是推之则思过半矣。心字难言。其义非一。有主理而言者。有主气而言者。如道心仁义之心。是理也。如人心食色之心。是气也。然则以理言之者。非心之本善乎。虽以气言之。如人心食色之心。亦未便可以不善目之也。何者。虽圣贤不能无人心。而惟精一于道。则是亦不害为善也。但本体固无不善。而流于不善。故斯为恶矣。然朱子所谓看来心有动静。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为说心之全体直指也。玩味有得。则当自知心字本意也。未知如何。明德朱子既曰良心则理为之主。故心亦从而良。气为之主。则未能良焉。此皆精微之极。非一时思虑所能洒然知得。切不可循人口气而遽为定论。必须积累穷究真实践履然后。也须有见处。恐不必率然争辨。徒有以病夫向里研几底工夫也。
质。不免有通塞偏全之异。譬如江河钟鼎之量。考其充满。则不能无大小浅深之分也。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是也。然则理同云者。非指有生之初。同禀是性之谓乎。理绝不同。非指有生之后。禀性偏全之谓乎。以是推之则思过半矣。心字难言。其义非一。有主理而言者。有主气而言者。如道心仁义之心。是理也。如人心食色之心。是气也。然则以理言之者。非心之本善乎。虽以气言之。如人心食色之心。亦未便可以不善目之也。何者。虽圣贤不能无人心。而惟精一于道。则是亦不害为善也。但本体固无不善。而流于不善。故斯为恶矣。然朱子所谓看来心有动静。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此为说心之全体直指也。玩味有得。则当自知心字本意也。未知如何。明德朱子既曰良心则理为之主。故心亦从而良。气为之主。则未能良焉。此皆精微之极。非一时思虑所能洒然知得。切不可循人口气而遽为定论。必须积累穷究真实践履然后。也须有见处。恐不必率然争辨。徒有以病夫向里研几底工夫也。[答金宪植]
问。大学以格物致知为最初用力。而不先之以居敬立本何也。朱子每以小学当之。若二学对言则固当。若专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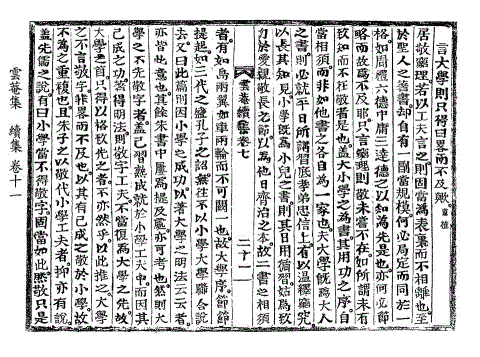 言大学则只得曰略而不及欤。(宪植)
言大学则只得曰略而不及欤。(宪植)居敬穷理。若以工夫言之。则固当为表里而不相离也。至于圣人之著书。却自有一副当规模。何必局定而同于一格。如周礼六德中庸三达德之以知为先是也。亦何必节略而故为不及耶。只言穷理则敬未尝不在。如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也。盖大小学之为书。其用功之序。自当相须。而非如他书之各自为一家也。夫大学既为大人之书。则必就平日所讲习底孝弟忠信上。有以温绎穷究。以长其知见。小学既为小儿之书。则其日用循习。姑为致力于爱亲敬长之节。以为他日齐治之本。故二书之相须者。有如鸟两翼如车两轮而不可阙一也。故大学序。节节提起。如三代之盛孔子之诏。无往不以小学大学联合说去。又曰此篇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云云者。亦皆此意也。其馀朱书中屡为提及处。亦可考也。然则大学之不先敬字者。盖已习熟成就于小学工夫中。而因其已成之功。著得明法。则敬字工夫。不当复为大学之先。故大学之首。只得以格致先之者。不亦然乎。以此推之。大学之不言敬字。非略而不及也。以其有已成之敬于小学。故不为之重复也。且朱子之以敬代小学工夫者。抑亦有说。盖先儒之说。有曰小学当不得敬字。固当如此。然敬只是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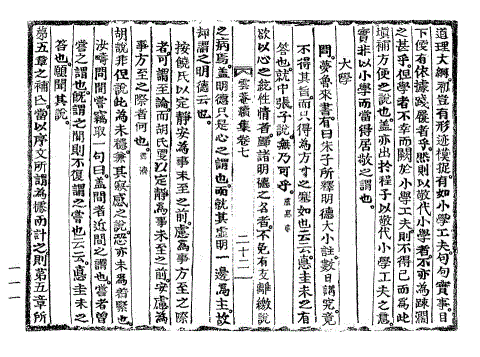 道理大纲。初岂有形迹模捉。有如小学工夫。句句实事。目下便有依据践履者乎。然则以敬代小学者。不亦为疏阔之甚乎。但学者不幸而阙于小学工夫。则不得已而为此填补方便之说也。盖亦出于程子以敬代小学工夫之意。实非以小学而当得居敬之谓也。
道理大纲。初岂有形迹模捉。有如小学工夫。句句实事。目下便有依据践履者乎。然则以敬代小学者。不亦为疏阔之甚乎。但学者不幸而阙于小学工夫。则不得已而为此填补方便之说也。盖亦出于程子以敬代小学工夫之意。实非以小学而当得居敬之谓也。大学
[答卢德圭]
问。梦鲁来书。有曰朱子所释明德大小注。数日讲究。竟不得其旨。而只得为方寸之塞如也云云。德圭未之有答也。就中张子说。无乃可乎。(卢德圭)
欲以心之统性情者。归诸明德之名者。不免有支离缴说之病焉。盖明德只是心之谓也。而就其虚明一边为主。故却谓之明德云也。
[答卢德济(三条)]
按饶氏以定静安为事未至之前。虑为事方至之际者。可谓至论。而胡氏更以定静为事未至之前。安虑为事方至之际者何也。(德济)
胡说非但说此为未稳。兼其寂感之说。恐亦未为着紧也。
汝畴问间尝窃取一句曰。盖间者近间之谓也。尝者曾尝之谓也。既谓之间则不复谓之尝也云云。德圭未之答也。愿闻其说。
第五章之补亡。当以序文所谓为据而计之。则第五章所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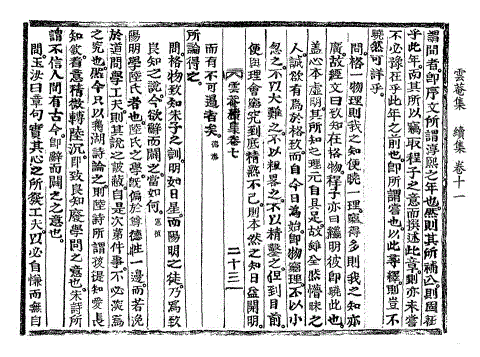 谓间者。即序文所谓淳熙之年也。然则其所补亡。则固在乎此年。而其所以窃取程子之意而撰述此章。则亦未尝不必豫在乎此年之前也。即所谓尝也。以此寻绎。则岂不晓然可详乎。
谓间者。即序文所谓淳熙之年也。然则其所补亡。则固在乎此年。而其所以窃取程子之意而撰述此章。则亦未尝不必豫在乎此年之前也。即所谓尝也。以此寻绎。则岂不晓然可详乎。问。格一物理则我之知便晓一理。穷得多则我之知亦广。故经文曰致知在格物。程子亦曰才明彼即晓此也。盖心本虚明。其所知之理元自具足。故虽全然懵昧之人。诚欲有为于格致。而自今日为始。即物穷理。不以小忽之。不以大难之。不以粗略之。不以精凿之。但到目前。便与理会穷究到底精熟不已。则本然之知日益开明。而有不可遏者矣。(德济)
所论得之。
[答金宪植]
问。格物致知朱子之训。明如日星。而阳明之徒。乃为致良知之说。今欲辞而辟之。当如何。(宪植)
阳明学陆氏者也。陆氏之学。既偏于尊德性一边。而若浼于道问学工夫。则其说之诐蔽。自是次第件事。不必深为之究也。然今只以鹅湖诗论之。则陆诗所谓孩提知爱长知钦。着意精微转陆沉。即致良知废学问之意也。朱诗所谓不信人间有古今。即辞而辟之之意也。
[答卢德济]
问。玉汝曰章句实其心之所发工夫。以必自慊而无自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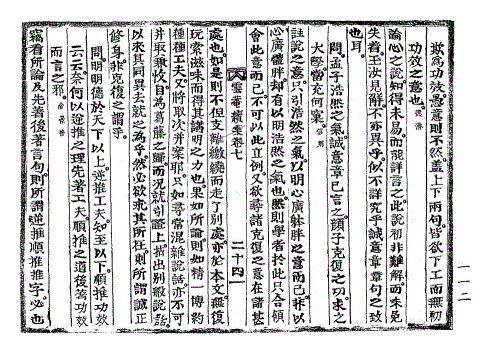 欺为功效。愚意则不然。盖上下两句。皆欲下工而无初功效之意也。(德济)
欺为功效。愚意则不然。盖上下两句。皆欲下工而无初功效之意也。(德济)论心之说。知得未易。而能详言之。此说初非难解。而未免失着。玉汝见解。不亦异乎。似不详究乎诚意章章句之致也耳。
[答卢信则]
问。孟子浩然之气。诚意章已言之。颜子克复之功。求之大学。当充何窠。(信则)
注说之意。只引浩然之气。以明心广体胖之意而已。非以心广体胖。却有以明浩然之气也。然则学者于此只合领会此意而已。不可以此立例。又欲寻诸克复之意在诸甚处也。如是则不但支离缴绕而走了别处。亦于本文。无复玩索滋味而得其讲明之力也。果如所论。则如精一博约种种工夫。又将取次并案耶。只如寻常混杂说话。亦不可并取兼收。自为葛藤之归。而况就引證上。拈出别般说话。以求其同异去就之为乎。然必欲求其所在。则所谓诚正修身。非克复之谓乎。
[答俞景善]
问。明明德于天下以上。逆推工夫。知至以下。顺推功效云云。奈何以逆推之理先著工夫。顺推之道后著功效而言之邪。(俞景善)
窃看所论及先著后著言句。则所谓逆推顺推推字。必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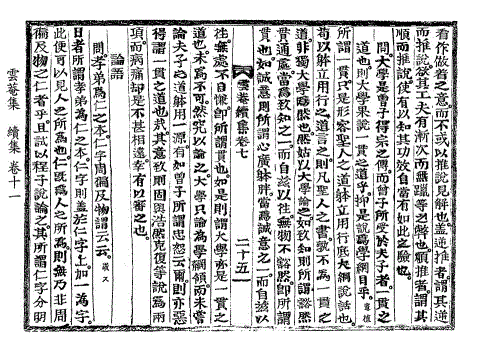 看作做着之意。而不或以推说见解也。盖逆推者。谓其逆而推说。欲其工夫有渐次而无躐等之弊也。顺推者。谓其顺而推说。使有以知其功效自当有如此之验也。
看作做着之意。而不或以推说见解也。盖逆推者。谓其逆而推说。欲其工夫有渐次而无躐等之弊也。顺推者。谓其顺而推说。使有以知其功效自当有如此之验也。[答金宪植]
问。大学是曾子得宗之传。而曾子所受于夫子者。一贯之道也。则大学果说一贯之道乎。抑是说为学纲目乎。(宪植)
所谓一贯。只是形容圣人之道体立用行底大纲说话也。苟以体立用行之道言之。则凡圣人之书。孰不为一贯之道。非独大学为然也。然姑以大学论之。如致知则所谓豁然贯通处。当为致知之一。而自玆以往。无物不豁然。即所谓贯也。如诚意则所谓心广体胖。当为诚意之一。而自玆以往。无处不自慊。即所谓贯也。如是则谓大学亦是一贯之道也。未为不可。然究以论之。大学只论为学纲领。而未尝论夫子之道体用一源。有如曾子所谓忠恕云尔。则亦恶得谓一贯之道也哉。其意致则固与浩然克复等说为两项。而病痛却是不甚相远。幸有以审之也。
论语
[答或人]
问。孝弟为仁之本。仁字周遍及物谓云云。(或人)
日者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仁字则盖于仁字上。加一为字。此便可以见人之所为也。仁既为人之所为。则无乃非周遍及物之仁者乎。且试以程子说论之。其所谓仁字分明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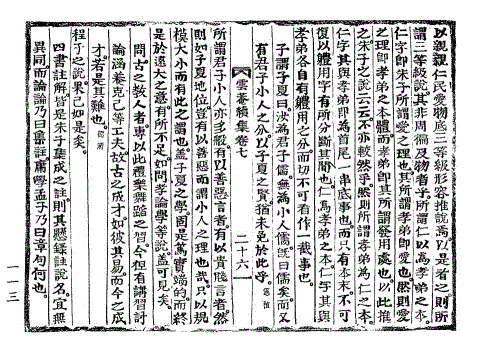 以亲亲仁民爱物底三等级形容推说焉。以是看之。则所谓三等级说。其非周遍及物者乎。所谓仁以为孝弟之本。仁字即朱子所谓爱之理也。其所谓孝弟即爱也。然则爱之理即孝弟之本体。而孝弟即其所谓发用处也。以此推之。朱子之说云云。不亦较然乎。然则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仁字其与孝弟即为首尾一串底事也。而只有本末。不可复以体用字有所分断其间也。仁为孝弟之本。仁字其与孝弟各自有体用之分。而切不可看作一截事也。
以亲亲仁民爱物底三等级形容推说焉。以是看之。则所谓三等级说。其非周遍及物者乎。所谓仁以为孝弟之本。仁字即朱子所谓爱之理也。其所谓孝弟即爱也。然则爱之理即孝弟之本体。而孝弟即其所谓发用处也。以此推之。朱子之说云云。不亦较然乎。然则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仁字其与孝弟即为首尾一串底事也。而只有本末。不可复以体用字有所分断其间也。仁为孝弟之本。仁字其与孝弟各自有体用之分。而切不可看作一截事也。[答金宪植]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既曰儒矣。而又有君子小人之分。以子夏之贤。犹未免于此乎。(宪植)
所谓君子小人亦多般。有以善恶言者。有以贵贱言者。然则如子夏地位。岂有以善恶而谓小人之理也哉。只以规模大小而有此之谓也。盖子夏之学。固是笃实端的。而终是于远大之意。有所不足。如问孝论学等说。盖可见矣。
[答卢德济(二条)]
问。古之教人者。专以此礼乐舞蹈之习。今但有讲习讨论涵养克己等工夫。故古之成才。如彼其易。而今之成才。若是其难也。(德济)
程子之说。果已如是矣。
四书注解。皆是朱子集成之注。则其悬录注说名。宜无异同。而论论乃曰集注。庸学孟子乃曰章句何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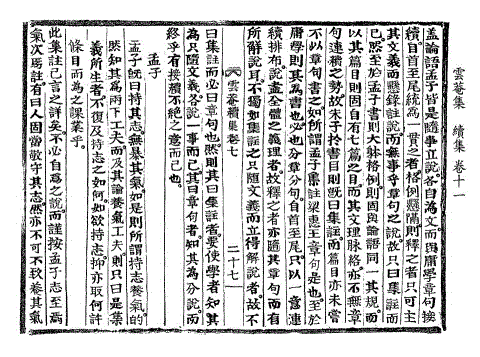 盖论语孟子皆是随事立说。各自为文。而与庸学章句接续。自首至尾统为一贯之者。格例悬隔。则释之者只可主其文义而悬录注说。而无事乎章句之说。故只曰集注而已。然至于孟子书则大体格例。则固与论语同一其规。而以其篇目则固自有七篇之目。而其文理脉络。亦不无章句连续之势。故朱子于书目则既曰集注。而篇目亦未尝不以章句书之。如所谓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是也。至于庸学则其为书也。必也分章分句。自首至尾。只以一意连续排布。说尽全体之义理者。故释之者亦随其章句而有所解说耳。不独如集注之只随文义而立得解说者。故不曰集注而必曰章句也。然则其曰集注者。要使学者知其为只随文义。各说一事而已。其曰章句者。知其为分说。而终乎有接续不绝之意而已也。
盖论语孟子皆是随事立说。各自为文。而与庸学章句接续。自首至尾统为一贯之者。格例悬隔。则释之者只可主其文义而悬录注说。而无事乎章句之说。故只曰集注而已。然至于孟子书则大体格例。则固与论语同一其规。而以其篇目则固自有七篇之目。而其文理脉络。亦不无章句连续之势。故朱子于书目则既曰集注。而篇目亦未尝不以章句书之。如所谓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是也。至于庸学则其为书也。必也分章分句。自首至尾。只以一意连续排布。说尽全体之义理者。故释之者亦随其章句而有所解说耳。不独如集注之只随文义而立得解说者。故不曰集注而必曰章句也。然则其曰集注者。要使学者知其为只随文义。各说一事而已。其曰章句者。知其为分说。而终乎有接续不绝之意而已也。孟子
[答卢德济(三条)]
孟子既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如是则所谓持志养气。的然知其为两下工夫。而及其论养气工夫。则只曰是集义所生者。不复及持志之如何。如欲持志。抑亦取何许条目而为之课业乎。
此集注已言之详矣。不必自为之说。而谨按孟子志至焉气次焉注。有曰人固当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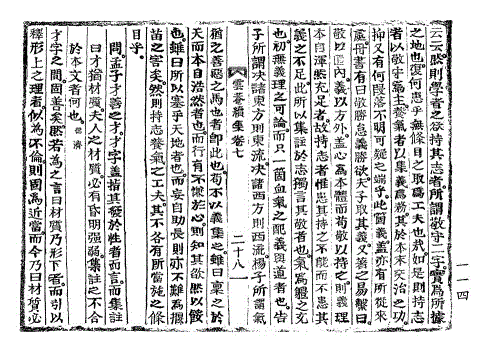 云云。然则学者之欲持其志者。所谓敬守二字。实为所据之地也。复何患乎无条目之取为工夫也哉。如是则持志者以敬守为主。养气者以集义为务。其于本末交治之功。抑又有何段落不明可疑之端乎。此个义。盖亦有所从来处。丹书有曰敬胜怠义胜欲。夫子取其义。又著之易系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盖心为本体而苟敬以持之。则义理本自浑然充足者。故持志者惟患其持之不能而不患其义之不足。此所以集注于志独言其敬者也。气为体之充也。初无义理之可论。而只一个血气之配义与道者也。告子所谓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杨子所谓气犹之善恶之马也者即此也。苟不以义集之。虽曰禀之于天而本自浩然者也。而行有不慊于心。则知其欿然以馁也。虽曰所以塞乎天地者也。而妄自助长则亦不难为揠苗之害矣。然则持志养气之工夫。其不各有所当施之条目乎。
云云。然则学者之欲持其志者。所谓敬守二字。实为所据之地也。复何患乎无条目之取为工夫也哉。如是则持志者以敬守为主。养气者以集义为务。其于本末交治之功。抑又有何段落不明可疑之端乎。此个义。盖亦有所从来处。丹书有曰敬胜怠义胜欲。夫子取其义。又著之易系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盖心为本体而苟敬以持之。则义理本自浑然充足者。故持志者惟患其持之不能而不患其义之不足。此所以集注于志独言其敬者也。气为体之充也。初无义理之可论。而只一个血气之配义与道者也。告子所谓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杨子所谓气犹之善恶之马也者即此也。苟不以义集之。虽曰禀之于天而本自浩然者也。而行有不慊于心。则知其欿然以馁也。虽曰所以塞乎天地者也。而妄自助长则亦不难为揠苗之害矣。然则持志养气之工夫。其不各有所当施之条目乎。问。孟子才善之才。才字盖指其发于性者而言。而集注曰才犹材质。夫人之材质。必有昏明强弱。集注之不合于本文者何也。(德济)
才字之问。固善矣。然若为之言曰材质乃形下者。而引以释形上之理者。似为不伦。则固为近当。而今乃曰材质必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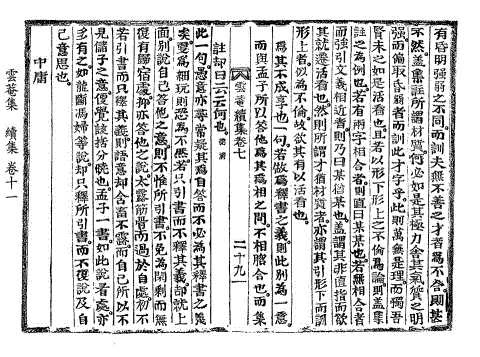 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训夫无不善之才者为不合。则甚不然。盖集注所谓材质。何必如是其极力舍其气质之明强。而偏取昏弱者而训此才字乎。此则万无是理。而独吾贤未之如是活看也。且若以形下形上之不伦为论。则盖集注之为例也。若有两字相合者。则直曰某某也。若无相合者而强引文义相近者。则乃曰某犹某也。盖谓其非直指而欲其就迁活看也。然则所谓才犹材质者。亦谓其引形下而训形上者。似为不伦。故欲其有以活看也。
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训夫无不善之才者为不合。则甚不然。盖集注所谓材质。何必如是其极力舍其气质之明强。而偏取昏弱者而训此才字乎。此则万无是理。而独吾贤未之如是活看也。且若以形下形上之不伦为论。则盖集注之为例也。若有两字相合者。则直曰某某也。若无相合者而强引文义相近者。则乃曰某犹某也。盖谓其非直指而欲其就迁活看也。然则所谓才犹材质者。亦谓其引形下而训形上者。似为不伦。故欲其有以活看也。为其不成享也一句。若做为释书之义。则此别为一意。而与孟子所以答他为其为相之问。不相吻合也。而集注却曰云云何也。(德济)
此一句。愚意亦寻常疑其为自答而不必为其释书之义矣。更为细玩则恐为不然。若只引书而不释其义。却就上面。别说自己答他之意。则不惟所引书。不免为闲剩而无复有归宿处。抑亦答他之说。太露筋骨而过于自处。初不若引书而只释其义。则语意却含畜不露。而自己所以不见储子之意。便觉该括分晓也。孟子一书。如此说看处。亦多有之。如龙断冯妇等说。却只释所引书。而不复说及自己意思也。
中庸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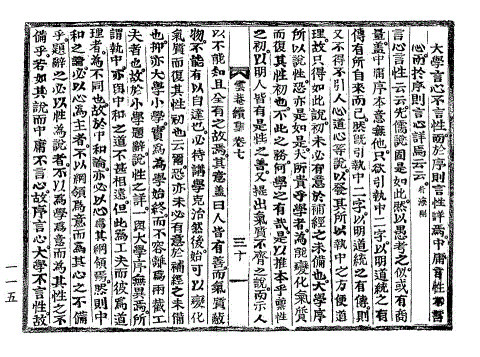 [答朴海刚]
[答朴海刚]大学言心不言性。而于序则言性详焉。中庸言性不言心。而于序则言心详焉云云。(朴海刚)
言心言性云云。先儒说固是如此。然以愚考之。似或有商量。盖中庸序本意无他。只欲引执中二字。以明道统之有传有所自来而已。然既引执中二字。以明道统之有传。则又不得不引人心道心等说。以发其所以执中之方便道理。故只得如此说。初未必有意于补经之未备也。大学序所以说性。恐亦是如是。夫所贵乎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复其性初也。不此之务。何学之有哉。是以推本乎禀性之初。以明人皆有是性之善。又提出气质不齐之说。而示人以不能知且全有之故焉。其意盖曰人皆有善。而气质蔽物。不能有以自达也。必待讲学克治然后。始可以变化气质而复其性初也云尔。恐亦未必有意于补经之未备也。抑亦大学小学。实为为学始终。而不容离为两截工夫者也。故于小学题辞。说性之详。一与大学序无异焉。所谓执中。亦与中和之道不甚相远。但此为工夫而彼为道理者。为不同也。故于中和论。亦必以心为其纲领焉。然则中和之论。必以心为主者。不以纲领为意而为其心之不备乎。题辞之必以性为说者。不以为学为意而为其性之不备乎。若如其说而中庸不言心。故序言心。大学不言性。故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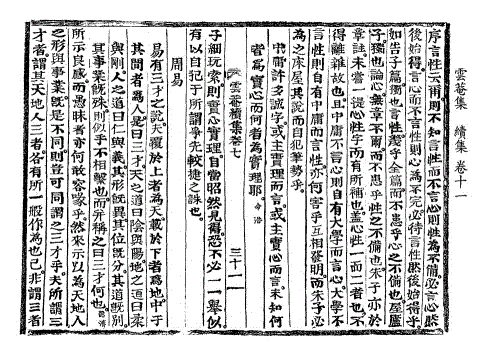 序言性云尔。则不知言性而不言心则性为不备。必言心然后始得。言心而不言性则心为不完。必待言性然后始得乎。如告子篇。独也言性。几乎全篇。而不患乎心之不备也。屋庐子。独也论心。无章不尔。而不患乎性之不备也。朱子亦于章注。未尝一提心性字而有所补也。盖心性一而二者也。不得离杂故也。且中庸不言心则自有大学而言心。大学不言性则自有中庸而言性。亦何害乎互相发明。而朱子必为之床屋其说而自犯笔势乎。
序言性云尔。则不知言性而不言心则性为不备。必言心然后始得。言心而不言性则心为不完。必待言性然后始得乎。如告子篇。独也言性。几乎全篇。而不患乎心之不备也。屋庐子。独也论心。无章不尔。而不患乎性之不备也。朱子亦于章注。未尝一提心性字而有所补也。盖心性一而二者也。不得离杂故也。且中庸不言心则自有大学而言心。大学不言性则自有中庸而言性。亦何害乎互相发明。而朱子必为之床屋其说而自犯笔势乎。[答杨命浩]
中庸许多诚字。或主实理而言。或主实心而言。未知何者为实心而何者为实理耶。(命浩)
子细玩索。则实心实理。自当昭然见得。恐不必一一举似。有以自犯于所谓争先较捷之诛也。
周易
[答卢德济]
易有三才之说。夫覆于上者为天。载于下者为地。中于其间者为人。是曰三才。天之道曰阴与阳。地之道曰柔与刚。人之道曰仁与义。其形既异。其位既分。其道既别。其事业既殊。则似乎不相系也。而并称之曰三才何也。(德济)
所示良感。而愚昧者亦何敢容喙乎。然来示以为天地人之形与事业。既是不同。则岂可同谓之三才乎。夫所谓三才者。谓其天地人三者。各有所一般作为也已。非谓三者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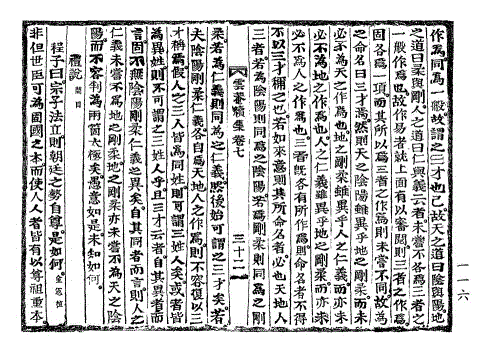 作为。同为一般。故谓之三才也已。故天之道曰阴与阳。地之道曰柔与刚。人之道曰仁与义云者。未尝不各为三者之一般作为也。故作易者就上面有以审阅。则三者之作为。固各为一项。而其所以为三者之作为则未尝不同。故为之命名曰三才焉。然则天之阴阳虽异乎地之刚柔。而未必不为天之作为也。地之刚柔虽异乎人之仁义。而亦未必不为地之作为也。人之仁义虽异乎地之刚柔。而亦未必不为人之作为也。三者既各有所作为。则命名者不得不以三才称之也。若如来意则其所命名者。必也天地人三者。若为阴阳则同为之阴阳。若为刚柔则同为之刚柔。若为仁义则同为之仁义。然后始可谓之三才矣。若夫阴阳刚柔仁义。各自为天地人之作为。则不容复以三才称焉。假人之三人皆为同姓。则可谓三姓人矣。或者皆为异姓。则不可谓之三姓人乎。且三才云者。自其异者而言。固不无阴阳刚柔仁义之异矣。自其同者而言。则人之仁义未尝不为地之刚柔。地之刚柔亦未尝不为天之阴阳。而不容判为两个太极矣。愚意如是。未知如何。
作为。同为一般。故谓之三才也已。故天之道曰阴与阳。地之道曰柔与刚。人之道曰仁与义云者。未尝不各为三者之一般作为也。故作易者就上面有以审阅。则三者之作为。固各为一项。而其所以为三者之作为则未尝不同。故为之命名曰三才焉。然则天之阴阳虽异乎地之刚柔。而未必不为天之作为也。地之刚柔虽异乎人之仁义。而亦未必不为地之作为也。人之仁义虽异乎地之刚柔。而亦未必不为人之作为也。三者既各有所作为。则命名者不得不以三才称之也。若如来意则其所命名者。必也天地人三者。若为阴阳则同为之阴阳。若为刚柔则同为之刚柔。若为仁义则同为之仁义。然后始可谓之三才矣。若夫阴阳刚柔仁义。各自为天地人之作为。则不容复以三才称焉。假人之三人皆为同姓。则可谓三姓人矣。或者皆为异姓。则不可谓之三姓人乎。且三才云者。自其异者而言。固不无阴阳刚柔仁义之异矣。自其同者而言。则人之仁义未尝不为地之刚柔。地之刚柔亦未尝不为天之阴阳。而不容判为两个太极矣。愚意如是。未知如何。礼说
[答金宪植(三条)]
程子曰。宗子法立。则朝廷之势自尊。是如何。(金宪植)
非但世臣可为固国之本。而使人人者皆有以尊祖重本。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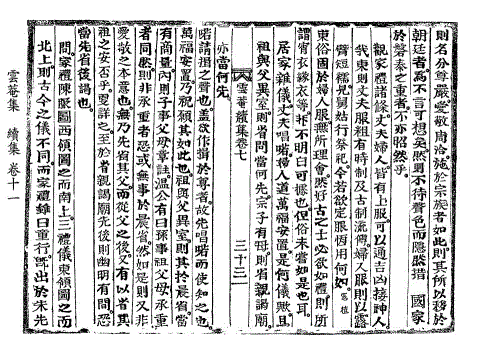 则名分尊严。爱敬周洽。施于宗族者如此。则其所以移于朝廷者。为不言可想矣。然则不待声色而隐然措 国家于磐泰之重者。不亦昭然乎。
则名分尊严。爱敬周洽。施于宗族者如此。则其所以移于朝廷者。为不言可想矣。然则不待声色而隐然措 国家于磐泰之重者。不亦昭然乎。观家礼诸条。丈夫妇人。皆有上服。可以通吉凶接神人。我东则丈夫服粗有时制及古制流传。妇人服则以露臂短襦。见舅姑行祭祀。今若欲定服恒用何如。(宪植)
东俗固于妇人服。无所理会。然好古之士必欲如礼。则所谓宵衣缘衣等。非不明白可据也。但俗未尝如是也耳。
居家杂仪。丈夫唱喏。妇人道万福安置。是何仪欤。且祖与父异室。则省问当何先。宗子有母。则省亲谒庙。亦当何先。
喏请揖之声也。盖欲作揖于尊者。故先唱喏而使知之也。万福安置。乃祝愿其如此也。祖与父异室。则其于晨省。当有商量。内则子事父母章注。温公有曰孙事祖父母承重者同然。则非承重者恐或无事于晨省。然如是则又非爱敬之本意也。无乃先省其父。而从父之后。又有以省其祖之安否乎。更详之。至于省亲谒庙先后则幽明有间。恐当先省后谒也。
[答郑得键]
问。家礼陈服图西领图之而南上。三礼仪东领图之而北上。则古今之仪不同。而家礼虽曰童行。既出于朱先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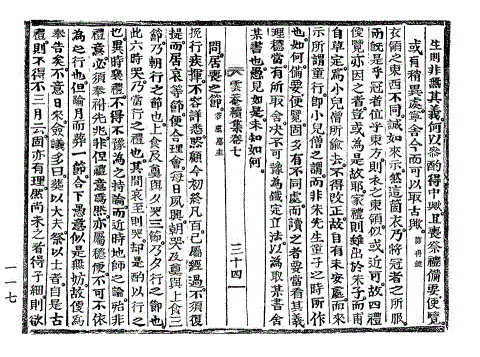 生则非无其义。何以参酌得中欤。且丧祭礼备要,便览。或有稍异处。宁舍今而可以取古欤。(郑得键)
生则非无其义。何以参酌得中欤。且丧祭礼备要,便览。或有稍异处。宁舍今而可以取古欤。(郑得键)衣领之东西不同。诚如来示。然这个衣。乃将冠者之所服。而既是乎冠者位乎东方。则衣之东领。似或近可。故四礼便览亦因之者。岂或为是故耶。家礼则虽出于朱子。而甫自草定。为小儿僧所偷去。不得改正。故自有未安处。而来示所谓童行。即小儿僧之谓。而非朱先生童子之时所作也。如何。备要,便览。固多有不同处。而读之者要当看其义理稳当。有所取舍。决不可豫为铁定立法。以为取某书舍某书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答卢德圭]
问。居丧之节。(答卢德圭)
挽行疾挥。不容详悉。然顾今初终凡百。已属经过。不须复提。而居哀等节。便合理会。每日夙兴。朝哭及奠与上食三节。乃朝行之节也。上食及奠与夕哭三节。乃夕行之节也。此六时哭。乃当行之礼也。其间哀至则哭。却是酌以行之也。异时襄礼。不得不豫为之持论。而近时地师之论。殆非礼意。必须奉祔先兆。非但礼意为然。亦属稳便。不可不依为之行也。但踰月而葬一节。合下愚意似是无妨。故便为奉告矣。不意日来。佥议多曰。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自是古礼。则不得不三月云。固亦有理。然尚未之看得子细。则欲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8H 页
 待追后详究然后。复为奉告可否。庶免失礼之诮也。
待追后详究然后。复为奉告可否。庶免失礼之诮也。[答卢德济]
问。铭旌之节。(答德济)
铭旌以通政书之则为违格。以折冲书之则为准格。非但人言如是。当日面破之说。不亦然乎。然伊时左右以为如是则纯为军资而无以见其为文资也。且洛下宰执之说。亦如是云。故只是听从而已。不谓今日却以傍人之说为执。而别有所纷纭也。
[答金羲铨]
问。灵几之节。(答金羲铨)
数段之示。极有理致。顾此孤陋。何所折衷而称答一二也哉。然陆学之持守严整。固非易及。而其主意则只靠尊德性一边。而于道问学上工夫。不屑致力。故义理见解。大段丑差。至谓学有顿悟而只是默坐澄心而已。如鹅湖诗所谓恐心传注还榛塞云云。是其学脉本张也。至若阳明。乃学陆者也。其学之地位浅深。在所不论。而范围来历则未必不为一般涂辙也。然则其于异学之目。王固不免。而陆亦不得以辞之也。来教以为朱子答陆书。有曰据礼小敛有席。至虞而有几筵。夫几筵与灵座。若非异名而同实。则葬有三月踰月之不同。而如是许久阙设。事甚未安。且以备要,便览考之。多所不合云。夫礼有古今沿革之异。若只靠后来制度以求合于古。则愈考而愈不同也。灵座几筵。固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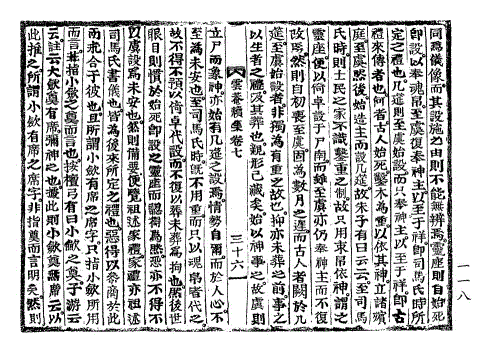 同为仪像。而其设施之由则不能无辨焉。灵座则自始死即设。以奉魂帛。至虞复奉神主。以至于祥。即司马氏时所定之礼也。几筵则至虞始设。而只奉神主。以至于祥。即古礼来传者也。何者。古人始死。凿木为重。以依其神。立诸殡庭。至虞然后。始造主而设几筵。故朱子有曰云云。至司马氏时。则士民之家不识凿重之制。故只用束帛依神。谓之灵座。便以倚卓设于尸南。而虽至虞亦仍奉神主而不复改焉。然则自初丧至虞。固为数月之迟。而古人者阙于几筵。至虞始设者。非独为有重之故也。抑亦未葬之前。事之以生者之礼。及其葬也。亲形已藏矣。始以神事之。故虞则立尸而象神。亦始有几筵之设焉。情势自尔。而于人心。不至为未安也。至司马氏时。既不用重。而只以魂帛者代之。故不得不预以倚卓代设。而不复以葬未葬为拘也。然后世眼目则惯于始死即设之灵座而认得为然。恐亦不得不以虞设为未安也。然则备要,便览祖述家礼。家礼亦祖述司马氏书仪也。皆为后来所定之礼也。恶得以参商于此而求合于彼也。且所谓小敛有席之席字。只指小敛所用而言。非指小敛之奠而言也。按檀弓有曰小敛之奠。子游云云。注云大敛奠有席。弥神之也。据此则小敛奠无席云。以此推之。所谓小敛有席之席字。非指奠而言明矣。然则
同为仪像。而其设施之由则不能无辨焉。灵座则自始死即设。以奉魂帛。至虞复奉神主。以至于祥。即司马氏时所定之礼也。几筵则至虞始设。而只奉神主。以至于祥。即古礼来传者也。何者。古人始死。凿木为重。以依其神。立诸殡庭。至虞然后。始造主而设几筵。故朱子有曰云云。至司马氏时。则士民之家不识凿重之制。故只用束帛依神。谓之灵座。便以倚卓设于尸南。而虽至虞亦仍奉神主而不复改焉。然则自初丧至虞。固为数月之迟。而古人者阙于几筵。至虞始设者。非独为有重之故也。抑亦未葬之前。事之以生者之礼。及其葬也。亲形已藏矣。始以神事之。故虞则立尸而象神。亦始有几筵之设焉。情势自尔。而于人心。不至为未安也。至司马氏时。既不用重。而只以魂帛者代之。故不得不预以倚卓代设。而不复以葬未葬为拘也。然后世眼目则惯于始死即设之灵座而认得为然。恐亦不得不以虞设为未安也。然则备要,便览祖述家礼。家礼亦祖述司马氏书仪也。皆为后来所定之礼也。恶得以参商于此而求合于彼也。且所谓小敛有席之席字。只指小敛所用而言。非指小敛之奠而言也。按檀弓有曰小敛之奠。子游云云。注云大敛奠有席。弥神之也。据此则小敛奠无席云。以此推之。所谓小敛有席之席字。非指奠而言明矣。然则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9H 页
 自大敛奠。始有席而弥神之。则至虞然后。始有几筵。固其次第也。盖制礼之本意以为始死。不忍遽乎以神事之。故只设重依神而已。其馈食则却如生设于下室。而不如今之上食于灵座也。愚见如是。未知是否。
自大敛奠。始有席而弥神之。则至虞然后。始有几筵。固其次第也。盖制礼之本意以为始死。不忍遽乎以神事之。故只设重依神而已。其馈食则却如生设于下室。而不如今之上食于灵座也。愚见如是。未知是否。[答或人]
问。大小敛及殡时。丧主首服之着当如何。(或人)
愚意则以为小敛时。主人兄弟着自布巾。以环绖视小敛。敛讫凭尸后。乃去白布巾环绖。括发加布头𢄼。至拜宾竟袭绖之时。自当依旧括发头𢄼。而只着首绖于其上焉。于此复以大敛亦环绖之说推之。则主人兄弟至大敛时。自当去括发头𢄼首绖。而复着白布巾环绖。待大敛后凭棺后。去白布巾环绖。而复着括发头𢄼首绖。至成服去之。至启殡。复着白布巾环绖以至卒哭。则似合礼意。
[答李承学]
古礼涂殡。必于正寝。今人家狭。殡于外舍。得无违于礼意乎。且于朝祖。只以魂帛代之。而若奉柩而朝出。自前户乎后户乎。(李承学)
正寝之殡。固是礼也。而房狭不能亦势也。无可奈何。恐不得不从便而殡于他房。朝祖则先儒固有奉帛代行之论矣。依而行之也。恐未为不可。所谕前后户。岂指殡宫之户乎。抑亦指祠堂之户乎。若指殡宫之户则却有商量。若以丧有进无退之礼推之。则其出也。自堂由前户。而顾今殡于外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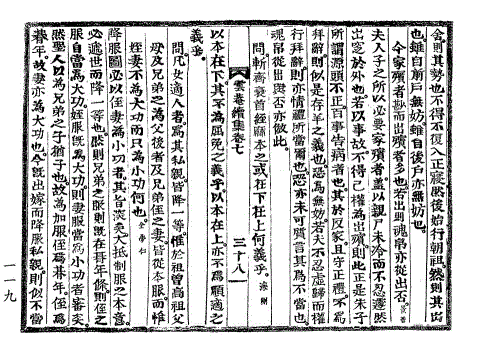 舍。则其势也不得不复入正寝然后始行朝祖。然则其出也。虽自前户无妨。虽自后户亦无妨也。
舍。则其势也不得不复入正寝然后始行朝祖。然则其出也。虽自前户无妨。虽自后户亦无妨也。[答俞景善]
今家殡者鲜而出殡者多也。若出则魂帛亦从出否。(景善)
夫人子之所以必要家殡者。盖以亲尸未冷而不忍遽然出窆于外也。若以事故。不得已权为出殡。则此正是朱子所谓源头不正。百事告病者也。其于反家。且守正礼。不为拜辞。则似是存羊之义也。恐为无妨。若夫不忍虚归而权行拜辞。则亦情礼所当尔也。恐亦未可质言其为不当也。魂帛从出与否亦仿此。
[答朴海刚]
问。斩齐衰首绖麻本之或在下在上何义乎。(海刚)
以本在下。其不为屈免之义乎。以本在上。亦不为顺适之义乎。
[答全梦仁]
问。凡女适人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惟于祖曾高祖父母及兄弟之为父后者及兄弟侄之妻。皆从本服。而惟侄妻不为大功而只为小功何也。(全梦仁)
降服图必以侄妻为小功者。其旨深矣。大抵制服之本意。必递世而降一等也。然则兄弟之服则既在期年条。则侄之服自当为大功。侄服既为大功。则妻服当为小功者审矣。然圣人以为兄弟之子犹子也。故为加服侄为期年。侄为期年。故妻亦为大功也。今既出嫁而降服私亲。则似不当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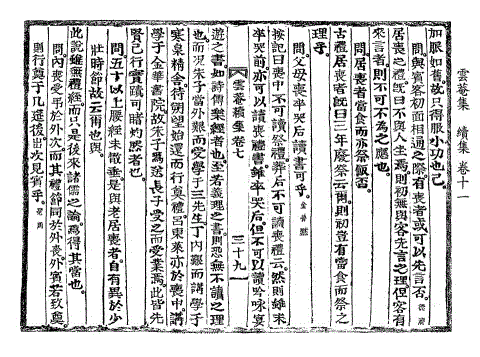 加服如旧。故只得服小功也已。
加服如旧。故只得服小功也已。[答卢德济(二条)]
问。与宾客初面相通之际。有丧者或可以先言否。(德济)
居丧之礼。既曰不与人坐焉。则初无与客先言之理。但客有来言者。则不可不为之应也。
问。居丧者当食而亦祭饭否。
古礼居丧者既曰三年废祭云尔。则初岂有当食而祭之理乎。
[答金善默(二条)]
问。父母丧卒哭后读书可乎。(金善默)
按记曰丧中不可读祭礼。葬后不可读丧礼云。然则虽未卒哭前。亦可以读丧礼书。虽卒哭后。但不可以读吟咏宴游之书。如诗传乐经者也。至若义理之书。则恐无不读之理也。而况朱子当外艰而受学于三先生。丁内艰而讲学于寒泉精舍。待朔望始还而行奠礼。吕东莱亦于丧中。讲学于金华书院。故朱子为送长子受之而受业焉。此皆先贤已行实迹可睹灼然者也。
问。五十以上腰绖未散垂。是与老居丧者。自有异于少壮时节故云尔也与。
此说虽无礼绖。而只是后来诸儒之论。为得其当也。
[答金冕周(二条)]
问。内丧受吊于外次。而其礼节同于外丧。外宾若致奠。则行奠于几筵后。出次见宾乎。(冕周)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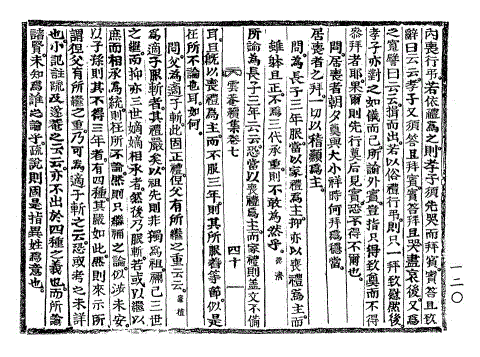 内丧行吊。若依礼为之。则孝子须先哭而拜宾。宾答且致辞曰云云。孝子又须答且拜宾。宾答拜且哭尽哀后。又为之宽譬曰云云。揖而出。若以俗礼行吊。则只一拜致慰然后。孝子亦对之如仪而已。所谕外宾。岂指只得致奠而不得参拜者耶。果尔则先行奠后见宾。恐不得不尔也。
内丧行吊。若依礼为之。则孝子须先哭而拜宾。宾答且致辞曰云云。孝子又须答且拜宾。宾答拜且哭尽哀后。又为之宽譬曰云云。揖而出。若以俗礼行吊。则只一拜致慰然后。孝子亦对之如仪而已。所谕外宾。岂指只得致奠而不得参拜者耶。果尔则先行奠后见宾。恐不得不尔也。问。居丧者朝夕奠与大小祥时何拜为稳当。
居丧者之拜。一切以稽颡为主。
[答卢德济]
问。为长子三年服。当以家礼为主。抑亦以丧礼为主。而虽体且正。不为三代承重。则不敢为然乎。(德济)
所谕为长子三年云云。恐当以丧礼为主。而家礼则盖文不备耳。且既以丧礼为主。而不服三年。则其所服着等节。似是在所不论也耳。如何。
[答金宪植]
问。父为适子斩。此固正礼。但父有所继之重云云。(宪植)
为适子服斩者。其礼严矣。以祖先则非独为祖。祢己三世之继。而抑亦三世嫡嫡相承者。然后乃服斩。若或以继以庶而相承为统。则在所不论。然则只继祢之论。似涉未安。以子孙则其不得三年者。有四种。其严如此。然则来示所谓但父有所继之重。乃可为适子斩之云。恐或考之未详也。小记注疏及遂庵之云云。亦不出于四种之义也。而所谕诸贤。未知为谁之论乎。疏说则固是指异姓为意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1H 页
 [答卢德圭(二条)]
[答卢德圭(二条)]问。葬有三月踰月之不同。如之何则可乎。(答德圭)
下苫有时。多少险逆。何以备经。奔问不得。尤极闷然。然除他。最是襄礼之限。尤合先为理会也。向书偬遽。未及审思。遽以踰月为告矣。及闻三月为可之说。则固为至论。盖不惟大夫三月而葬之说。明为證据。抑亦所谓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云者。未尝不为今日准备也。然士大夫之分。亦未能分晓。故考诸大典。则盖自九品至五品则皆合为士。而至若四品则乃所谓士初试为大夫者也。然考诸传记。则所谓朝奉,朝散。乃为四品。而或有以郎书之之处焉。岂古者亦或以士待之。而不必于大夫之充位乎。此未可知也。然则先大夫之职。若涉四品。则其于襄礼。以三月为定者固当也。然又不能无疑者。周礼为大夫者若至七命八命。则未尝不为诸侯而未就国。则只以大夫自处而不用诸侯之礼也。盖以其徒有诸侯之位。而实无诸侯土地人民故也。且如政和之礼。宋之大夫虽有诸侯之位而无其国者。皆不用诸侯之礼。而朱子是之也。以此推之。虽为大夫而未尝行公当职。则皆未可以大夫为礼也。而至于先大夫。则其于四三品职。皆已行公举职。则恐当以大夫之礼行之也。然则传之者为曰似以腊月初二日粗为初择云。未知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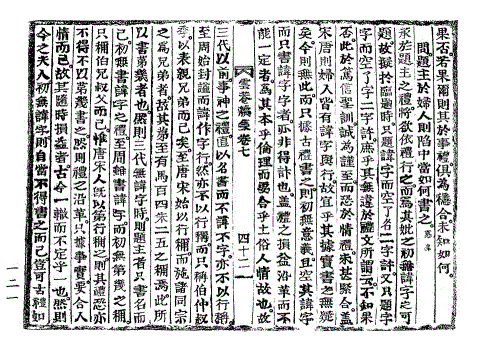 果否。若果尔则其于事礼。俱为稳合。未知如何。
果否。若果尔则其于事礼。俱为稳合。未知如何。问。题主于妇人则陷中当如何书之。(德圭)
承于题主之礼。将欲依礼行之。而为其妣之初无讳字之可题。故拟于临题时。只题讳字而空了名二字许。又只题字字而空了字二字许。庶乎其无违于礼文所谓云。不知果否。此于笃信圣训。诚为谨至。而恐于情礼。未甚紧合。盖宋唐则妇人皆有讳字与行。故宜乎其据实书之无疑矣。今则无此。而只据古礼书之。则初无意义。且空其讳字而只书讳字字者。亦非得计也。盖礼之损益沿革而不能一定者。为其本乎伦理而要合乎土俗人情故也。故三代以前。事神之礼。直以名书而不讳不字。亦不以行称。至周始封谥而讳作字行。然亦不以行称。而只称伯仲叔季。以表亲兄弟而已矣。至唐宋始以行称。而施诸同宗之为兄弟者。故其第至有马百四朱二五之称焉。此所以书第几者也。然则三代无讳字时。则题主者只书名而已。初无书讳字之礼。至周虽书讳字。而初无第几之称。只称伯兄叔父而已。惟唐宋人既以第行称之。则其礼恐亦不得不以第几书之。然则礼之沿革。只据事实。要合人情而已。故其随时损益者。古今一辙而不定乎一也。然则今之夫人。初无讳字。则自当不得书之而已。岂可古礼如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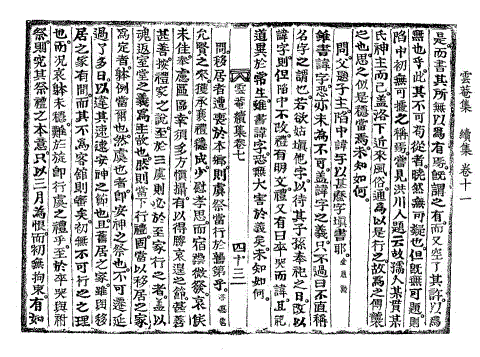 是。而书其所无以为有焉。既谓之有。而又空了其许。以为无也乎。此其不可苟从者。晓然无可疑也。但既无可题。则陷中初无可据之称焉。尝见洪川人题云故孺人某贯某氏神主而已。盖洛下近来风俗。通为以是行之。故为之传袭之也。思之似是稳当焉。未知如何。
是。而书其所无以为有焉。既谓之有。而又空了其许。以为无也乎。此其不可苟从者。晓然无可疑也。但既无可题。则陷中初无可据之称焉。尝见洪川人题云故孺人某贯某氏神主而已。盖洛下近来风俗。通为以是行之。故为之传袭之也。思之似是稳当焉。未知如何。[答金履勋]
问。父题子主。陷中讳字以甚么字填书耶。(金履勋)
虽书讳字。恐亦未为不可。盖讳字之义。只不过曰不直称名字之谓也。若欲姑填他字。以待其子孙奉祀之日。改以讳字。则但陷中不改。礼有明文。礼又有曰卒哭而讳。且祀道异于常生。虽书讳字。恐无大害于义矣。未知如何。
[答卢德圭]
问。移居者遭丧于本乡。则虞祭当行于旧第乎。(答德圭)
允贤之来。获承襄礼稳成。少慰孝思。而宿祟微发。哀候未佳。奉虑区区。幸须多方慎摄。有以得胜哀遑之节。甚善甚善。按礼家之说。至于三虞则必于至家行之者。盖以魂返室堂之义为主故也。然则当下行礼。固当以移居之家为定者。体例当尔也。然虞也者。即安神之祭也。不可迁延过了多日。以违其速速安神之节也。且旧居之家。虽与移居之家有间。而其不为客馆则审矣。初无不可行之之理也。而况哀体未稳。难于旋即行虞之礼乎。至于卒哭与祔祭。则究其祭礼之本意。只以三月为恨。而初无拘束。有如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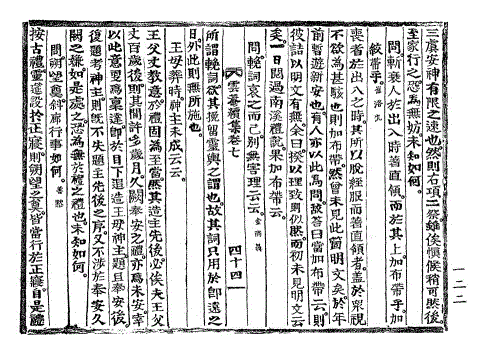 三虞安神有限之速也。然则右项二祭。虽俟慎候稍可然后。至家行之。恐为无妨。未知如何。
三虞安神有限之速也。然则右项二祭。虽俟慎候稍可然后。至家行之。恐为无妨。未知如何。[答崔洛九]
问。斩衰人于出入时著直领。而于其上。加布带乎。加绞带乎。(崔洛九)
丧者于出入之时。其所以脱绖服而著直领者。盖于众视不欲为甚骇也则加布带。然曾未见此个明文矣。于年前暂游新安也。有人亦以此为问。故答曰当加布带云。则彼诘以明文有无。余曰。揆以理致则似然。而初未见明文云矣。一日阅过南溪礼说。果加布带云。
[答金尚义(二条)]
问。挽词哀之而已。别无害理云云。(金尚义)
所谓挽词。欲其挽留灵舆之谓也。故其词只用于即远之日。外此则无所施也。
王母葬时。神主未成云云。
王父丈教意。于礼固为至当。然其造主先后。必俟夫王父丈百岁后。则其间许多岁月。久阙奉安之礼。亦为未安。幸以此意更为禀达。即于目下追造王母神主。题且奉安后。复题考神主。则既不失题主先后之序。又不涉于奉安久阙之嫌。如是处之。恐为无于礼之礼也。未知如何。
[答金善默]
问。朔望奠。斜廊行事如何。(善默)
按古礼。灵筵设于正寝。则朔望之奠。皆当行于正寝。自是礼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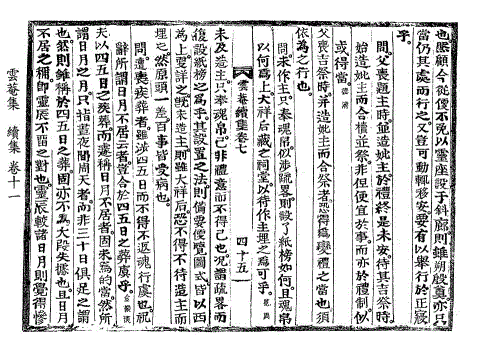 也。然顾今从便不免以灵座设于斜廊。则虽朔殷奠。亦只当仍其处而行之。又岂可动辄移安。要有以举行于正寝乎。
也。然顾今从便不免以灵座设于斜廊。则虽朔殷奠。亦只当仍其处而行之。又岂可动辄移安。要有以举行于正寝乎。[答卢德济]
问。父丧题主时。并造妣主。于礼终是未安。待其吉祭时。始造妣主而合椟并祭。非但便宜于事。而亦于礼制。似或得当。(德济)
父丧吉祭时。并造妣主而合祭者。恐得为变礼之当也。须依为之行也。
[答金冕周]
问。未作主。只奉魂帛。似涉疏略。则设了纸榜如何。且魂帛以何为上。大祥后藏之祠堂。以待作主埋之为可乎。(冕周)
未及造主。只奉魂帛。已非礼意而不得已也。况谓疏略而复设纸榜之为乎。其设置之法。则备要便览图式。皆以西为上。更详之。既未造主。则虽大祥后。恐不得不待造主而埋之。然原头一差。百事皆受病也。
[答金振瑛]
问。遭丧疾葬者。虽涉四五日而不得不返魂行虞也。祝辞所谓日月不居云者。岂合于四五日之葬虞乎。(金振瑛)
夫以四五日之疾葬。而遽称日月不居者。固未为的当。然所谓日月之月。只指昼夜间周天者。而非三十日俱足之谓也。然则虽称于四五日之葬。固亦不为大段失据也。且日月不居之称。即灵辰不留之对也。灵辰较诸日月则觉得惨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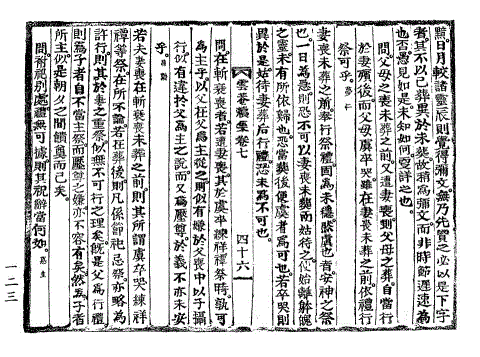 黯。日月较诸灵辰则觉得弥文。无乃先贤之必以是下字者。其不以已葬异于未葬。故稍为弥文。而非时节迟速为也否。愚见如是。未知如何。更详之也。
黯。日月较诸灵辰则觉得弥文。无乃先贤之必以是下字者。其不以已葬异于未葬。故稍为弥文。而非时节迟速为也否。愚见如是。未知如何。更详之也。[答全梦仁]
问。父母之丧未葬之前。又遭妻丧。则父母之葬。自当行于妻殡后。而父母虞卒哭。虽在妻丧未葬之前。依礼行祭可乎。(梦仁)
妻丧未葬之前。奉行祭礼。固为未稳。然虞也者。安神之祭也。一日为急。则恐不可以妻丧未葬而姑待之。使始离体魄之灵。未有所依归也。恐当葬后便虞者为可也。若卒哭则异于是。姑待妻葬后行礼。恐未为不可也。
[答金履勋]
问。在斩衰丧者。若遭妻丧。其于虞卒练祥禫祭时。孰可为主乎。以父在父为主从之。则似有嫌于父丧中以子摄行。似有违于父为主之说。而又为压尊。于义不亦未安乎。(履勋)
若夫妻丧在斩衰丧未葬之前。则其所谓虞卒哭练祥禫等祭。在所不论。若在葬后。则凡系节祀忌祭。亦略为许行。则其于妻之重祭。似无不可行之理矣。既是父为行礼。则为子者自不当主祭。而压尊之嫌。亦不容有矣。然为子者所主。似是朝夕之间馈奠而已矣。
[答虑德圭(七条)]
问。祔祀别处。礼无可据。则其祝辞当何如。(德圭)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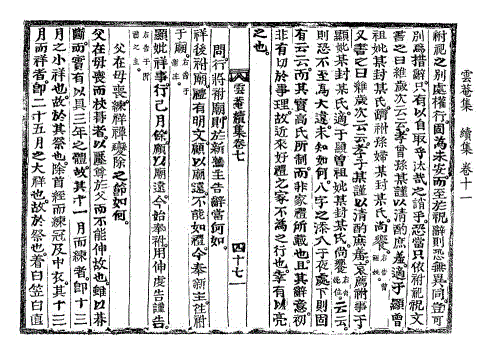 祔祀之别处权行。固为未安。而至于祝辞则恐无异同。岂可别为措辞。只有以自取乎汰哉之诮乎。恐当只依祔祀祝文书之曰维岁次云云。孝曾孙某谨以清酌庶羞。适于显曾祖妣某封某氏。跻祔孙妇某封某氏。尚飨。(右告曾祖妣。)
祔祀之别处权行。固为未安。而至于祝辞则恐无异同。岂可别为措辞。只有以自取乎汰哉之诮乎。恐当只依祔祀祝文书之曰维岁次云云。孝曾孙某谨以清酌庶羞。适于显曾祖妣某封某氏。跻祔孙妇某封某氏。尚飨。(右告曾祖妣。)又书之曰维岁次云云。孝子某谨以清酌庶羞。哀荐祔事于显妣某封某氏。适于显曾祖妣某封某氏。尚飨(右告妣位。)云云。则恐不至为大违。未知如何。八字之添入于夜处下则固有云云。而其实高氏所制。而非家礼所载也。且其辞意。初非有切于事理。故近来好礼之家不为之行也。幸有以亮之也。
问。行将祔庙。则于新旧主告辞当何如。
祥后祔庙。礼有明文。顾以庙远。不能如礼。今奉新主。往祔于庙。(右告于新主。)
显妣祥事。行已月馀。顾以庙远。今始奉祔。用伸虔告谨告。(右告于所祔之主。)
父在母丧。练祥禫变除之节如何。
父在母丧而杖期者。以压尊于父而不能伸故也。虽以期断。而实有以具三年之体。故其十一月而练者。即十三月之小祥也。故于其祭也。除首绖而练冠及中衣。其十三月而祥者。即二十五月之大祥也。故于祭也。着白笠白直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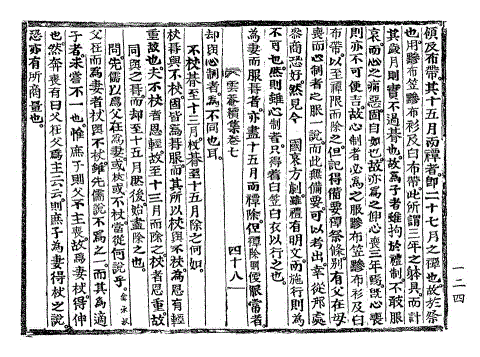 领及布带。其十五月而禫者。即二十七月之禫也。故于祭也。用黪布笠黪布衫及白布带。此所谓三年之体具。而计其岁月则实不过期也。故为子者虽拘于礼制。不敢服哀。而心之痛恶。固自如也。故亦为之伸心丧三年焉。既心丧则亦不可便吉。故心制者必为之服黪布笠黪布衫及白布带。以至禫限而除之。但记得备要禫祭条。别有父在母丧而心制者之服一说。而此无备要。可以考出。幸从那处参商恐好。然见今 国哀方剧。虽礼有明文。而施行则为不可也。然则虽心制者。只得着白笠白衣以行之也。
领及布带。其十五月而禫者。即二十七月之禫也。故于祭也。用黪布笠黪布衫及白布带。此所谓三年之体具。而计其岁月则实不过期也。故为子者虽拘于礼制。不敢服哀。而心之痛恶。固自如也。故亦为之伸心丧三年焉。既心丧则亦不可便吉。故心制者必为之服黪布笠黪布衫及白布带。以至禫限而除之。但记得备要禫祭条。别有父在母丧而心制者之服一说。而此无备要。可以考出。幸从那处参商恐好。然见今 国哀方剧。虽礼有明文。而施行则为不可也。然则虽心制者。只得着白笠白衣以行之也。为妻而服期者。亦尽十五月而禫除。但禫除则便服常者。却与心制者。为不同也耳。
不杖期至十三月。杖期至十五月除之何如。
杖期与不杖。固皆为期服。而其所以杖与不杖。为恩有轻重故也。夫不杖者恩轻。故至十三月而除之。杖者恩重。故 同与之期。而却至十五月然后。始尽除之也。
[答金永叔]
问。先儒以为父在为妻。或杖或不杖。当从何说乎。(金永叔)
父在而为妻者杖与不杖。虽先儒说不为之一。而其为适子者。未尝不一也。惟庶子则父不主丧。故为妻杖。得伸也。然奔丧有曰父在父为主云云。则庶子为妻得杖之说。恐亦有所商量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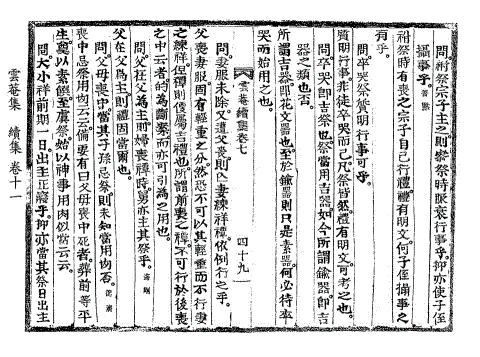 [答金善默(四条)]
[答金善默(四条)]问。祔祭宗子主之。则参祭时服衰行事乎。抑亦使子侄摄事乎。(善默)
祔祭时有丧之宗子自己行礼。礼有明文。何子侄摄事之有乎。
问。卒哭祭质明行事可乎。
质明行事。非徒卒哭而已。凡祭皆然。礼有明文。可考之也。
问。卒哭即吉祭也。祭当用吉器。如今所谓鍮器。即吉器之类也否。
所谓吉器。即花文器也。至于鍮器则只是素器。何必待卒哭而始用之也。
问。妻服未除。又遭父丧。则亡妻练祥禫。依例行之乎。
父丧妻服。固有轻重之分。然恐不可以其轻重而不行妻之练祥。但禫则便属吉礼也。所谓前丧之禫。不可行于后丧之中云者。的为断案。而亦可引为之用也。
[答朴海刚]
问。父在父为主。则妇丧禫时。舅亦主其祭乎。(海刚)
父在父为主。则礼固当尔也。
[答卢德济(二条)]
问。父母丧中。当其子孙忌祭。则未知当用肉否。(德济)
丧中忌祭用肉云云。备要有曰父母丧中死者。葬前等平生。奠以素馔。至虞祭。始以神事用肉似当云云。
问。大小祥前期一日。出主正寝乎。抑亦当其祭日出主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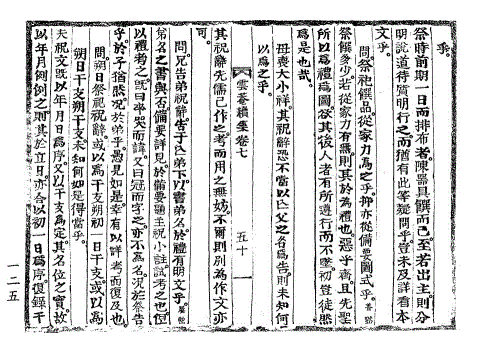 乎。
乎。祭时前期一日而排布者。陈器具馔而已。至若出主。则分明说道待质明行之。而犹有此等疑问乎。岂未及详看本文乎。
[答金善默(二条)]
问。祭祀馔品。从家力为之乎。抑亦从备要图式乎。(善默)
祭馔多少。若从家力有无。则其于为礼也。恶乎齐。且先圣所以为礼为图。欲其后人者有所遵行而不坠。初岂徒然为是也哉。
母丧大小祥。其祝辞恐不当以亡父之名为告。则未知何以为之乎。
其祝辞先儒已作之。考而用之无妨。不尔则别为作文亦可。
[答金履勋(三条)]
问。兄告弟祝辞。告于亡弟下。以书弟名。于礼有明文乎。(履勋)
弟名之书与否。备要详见。于备要题主祝小注。试考之也。但以礼考之。既曰卒哭而讳。又曰冠而字之。亦不为名。况于祭告乎。于子犹然。况于弟乎。愚见如是。幸有以详考而复及也。
问。朔日祭祀祝辞。或以为干支朔初一日干支。或以为朔日干支朔干支。未知何如是得当乎。
夫祝文既以年月日为序。又以干支为定。其名位之实。故以年月例例之。则其于立日。亦合以初一日为序。复录干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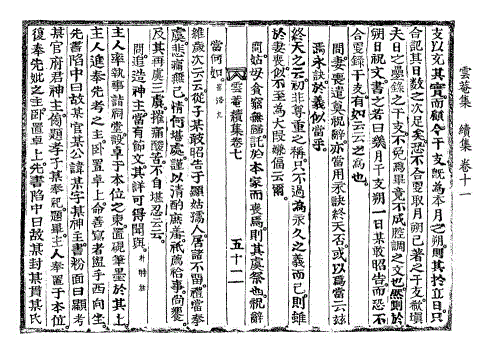 支以充其实。而顾今干支既为本月之朔。则其于立日。只合记其日数之次足矣。恐不合更取月朔已著之干支。欷填夫日之叠录之干支。不免为毕竟不成腔调之文也。然则于朔日祝文。书之若曰几月干支朔一日某敢昭告。而恐不合更录干支。有如云云之为也。
支以充其实。而顾今干支既为本月之朔。则其于立日。只合记其日数之次足矣。恐不合更取月朔已著之干支。欷填夫日之叠录之干支。不免为毕竟不成腔调之文也。然则于朔日祝文。书之若曰几月干支朔一日某敢昭告。而恐不合更录干支。有如云云之为也。问。妻丧遣奠祝辞。亦当用永诀终天否。或以为当云玆焉永诀。于义似当乎。
终天之云。初非尊重之称。只不过为永久之义而已。则虽于妻丧。似不至为大段嫌偪云尔。
[答崔洛九]
问。姑母贫穷无归。托于本家而丧焉。则其虞祭也。祝辞当何如。(崔洛九)
维岁次云云。从子某敢昭告于显姑孺人。居诸不留。礼当奉虞。悲痛无已。情何堪处。谨以清酌庶羞。祇荐祫事。尚飨。及其再虞三虞。摧痛酸苦。不自堪忍云云。
[答朴时柱(二条)]
问。追造神主。当有节文。其详可得闻与。(朴时柱)
主人率执事诣祠堂。设卓于本位之东。置砚笔墨于其上。主人进奉先考之主。卧置卓上。命善写者盥手西向坐。先书陷中曰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神主。书粉面曰显考某官府君神主。傍题孝子某奉祀。题毕。主人奉置于本位。复奉先妣之主。卧置卓上。先书陷中曰故某封某贯某氏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6L 页
 神主。粉面曰显妣某封某氏神主。傍题上同。主人奉置于本位。○主人就高祖考以下诸位前。焚香斟酒讫。祝执板立于主人之左。主人以下皆跪。读曰○维云云。玄孙某敢昭告于显高祖考某官府君,显高祖妣某封某氏。以下至显祖考某官府君,显祖妣某封某氏皆列书。玆以先考某官府君,先妣某封某氏神主未成。今始追造。题奉如仪。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告毕。在位者皆再拜。○仍就考妣位前。焚香斟酒。祝跪读曰维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显考某官府君,显妣某封某氏。曩于襄礼。事势偬遽。未奉神主。今始追造。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毕。主人以下皆再拜。纳主辞神以退。
神主。粉面曰显妣某封某氏神主。傍题上同。主人奉置于本位。○主人就高祖考以下诸位前。焚香斟酒讫。祝执板立于主人之左。主人以下皆跪。读曰○维云云。玄孙某敢昭告于显高祖考某官府君,显高祖妣某封某氏。以下至显祖考某官府君,显祖妣某封某氏皆列书。玆以先考某官府君,先妣某封某氏神主未成。今始追造。题奉如仪。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告毕。在位者皆再拜。○仍就考妣位前。焚香斟酒。祝跪读曰维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显考某官府君,显妣某封某氏。曩于襄礼。事势偬遽。未奉神主。今始追造。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毕。主人以下皆再拜。纳主辞神以退。追造妣位神主祝辞。
维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显妣某封某氏。往于襄礼。神主未成。悚罪无地。今始造成。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
代答朔州校宫修庙问目(详见答通)
移安祝辞未知如何。若有佳作。则详录指示事。
移安祝初不过以重修之意。措数语告移安而已。何必佳作之为也。况班门弄斧。虽愚亦耻其为未莹也。然好问之盛。必欲使之效愚。则有一焉。其于东庑西庑。各自为一祝而云云。敢昭告于某先生。(以下列书。)伏以墙宇颓圮。今将改筑。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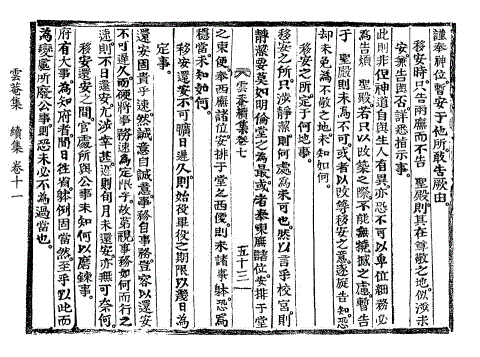 谨奉神位。暂安于他所。敢告厥由。
谨奉神位。暂安于他所。敢告厥由。移安时。只告两庑而不告 圣殿。则其在尊敬之地。似涉未安。兼告与否。详悉指示事。
此则非但神道自与生人有异。亦恐不可以卑位细务必为告烦 圣殿。若只以改筑之际。不能无挠撼之虑。暂告于 圣殿则未为不可。或者以改筑移安之意。逐旋告知。恐却未免为不敬之地。未知如何。
移安之所。定于何地事。
移安之所。只涉静洁。则何处为未可也。然以言乎校宫。则静洁要莫如明伦堂之为最。或者奉东庑诸位。安排于堂之东便。奉西庑诸位。安排于堂之西便。则求诸事体。恐为稳当。未知如何。
移安还安。不可旷日迟久。则始役毕役之期限以几日为定事。
还安固贵乎速。然诚意自诚意。事务自事务。岂容以还安不可迟久。而硬将事务速为定限乎。故第视事务如何而行之速。则不日还安。尤涉幸甚。迟则旬月未还安。亦无可奈何。
移安还安之间。官处所与公事未知何以磨鍊事。
府有大事。为知府者。间日往省。体例固当然。至乎以此而为变处所废公事。则恐未必不为过当也。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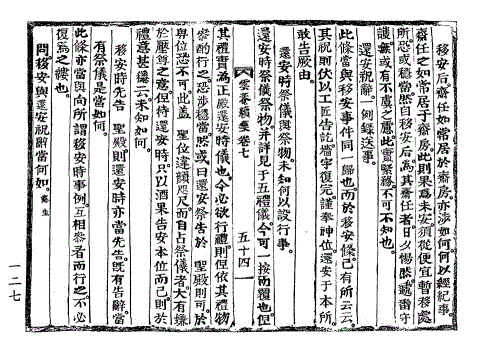 移安后。斋任如常居于斋房。亦涉如何。何以经纪事。
移安后。斋任如常居于斋房。亦涉如何。何以经纪事。斋任之如常居于斋房。此则果为未安。须从便宜暂移处所。恐或稳当。然自移安后。为其斋任者。日夕惕然。递番守护。无或有不虞之虑。此实紧务。不可不知也。
还安祝辞。一例录送事。
此条当与移安事件同一归也。而于移安条。已有所云云。其祝则伏以工匠告讫。墙宇复完。谨奉神位。还安于本所。敢告厥由。
还安时祭仪与祭物。未知何以设行事。
还安时祭仪祭物。并详见于五礼仪。今可一按而覆也。但其礼实为正殿还安时仪也。今必欲行礼。则但依其礼物参酌行之。恐涉稳当。然或曰还安祭告于 圣殿则可。于畀位恐不可。此盖 圣位违颜咫尺。而自占祭仪者。大有嫌于压尊之意。但待还安时。只以酒果告安本位而已。则于礼意甚稳云。未知如何。
移安时先告 圣殿。则还安时亦当先告。既有告辞。当有祭仪是当如何。
此条亦当与向所谓移安时事例。互相参看而行之。不必复为之缕也。
[答虑德圭(二条)]
问。移安与还安祝辞当何如。(德圭)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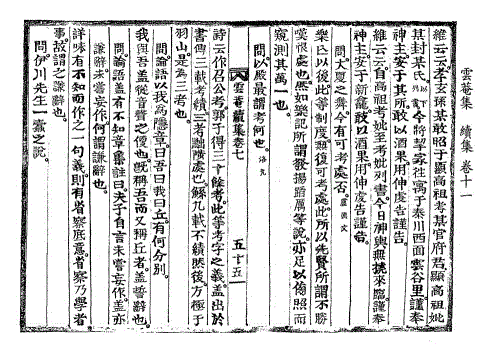 维云云。孝玄孙某敢昭于显高祖考某官府君,显高祖妣某封某氏。(以下列书。)今将挈家往寓于泰川西面云谷里。谨奉神主。安于其所。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
维云云。孝玄孙某敢昭于显高祖考某官府君,显高祖妣某封某氏。(以下列书。)今将挈家往寓于泰川西面云谷里。谨奉神主。安于其所。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维云云。自高祖考妣至考妣列书。今日神舆无挠来临。谨奉神主。安于新龛。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
[答虑德文]
问。大夏之舞。今有可考处否。(卢德文)
乐亡以后。此等制度。无复可考处。此所以先贤所谓不胜叹恨处也。然如乐记所谓发扬蹈厉等说。亦足以傍照而窥测其万一也。
[答崔洛九(四条)]
问。以殿最谓考何也。(洛九)
诗云作召公考。郭子得三十馀考。此等考字之义。盖出于书传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处也。鲧九载不绩然后。方极于羽山。是为三考也。
问。论语以我为隐章。曰吾曰我曰丘。有何分别。
我与吾盖从音声之便也。既称吾而又称丘者。盖誓辞也。
问。论语盖有不知章集注曰。夫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未尝妄作。何谓谦辞也。
详味有不知而作之一句义。则有省察底意。省察乃学者事。故谓之谦辞也。
问。伊川先生一蠹之说。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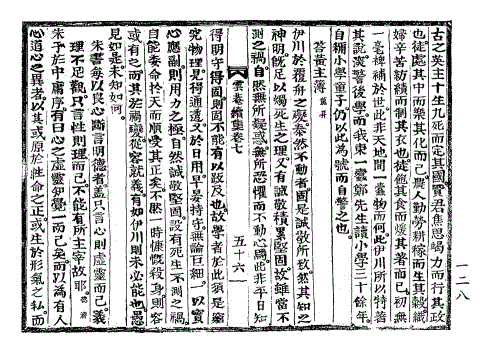 古之英主十生九死而定其国。贤君焦思竭力而行其政也。徒处其中而乐其化而已。农人勤劳耕稼而生其谷。织妇辛苦纺绩而制其衣也。徒饱其食而煖其著而已。初无一毫裨补于世。此非天地间一蠹物而何。此伊川所以特著其说。深警后学。而我东一蠹郑先生读小学三十馀年。自称小学童子。仍以此为号而自警之也。
古之英主十生九死而定其国。贤君焦思竭力而行其政也。徒处其中而乐其化而已。农人勤劳耕稼而生其谷。织妇辛苦纺绩而制其衣也。徒饱其食而煖其著而已。初无一毫裨补于世。此非天地间一蠹物而何。此伊川所以特著其说。深警后学。而我东一蠹郑先生读小学三十馀年。自称小学童子。仍以此为号而自警之也。答黄主簿(龙升)
伊川于覆舟之变。泰然不动者。固是诚敬所致。然其知之神明。既足以烛死生之理。又有诚敬积累坚固。故虽当不测之祸。自然无所疑惑。无所恐惧而不动心焉。此非平日知得明守得固。则固不能有以跂及也。故学者于此须是穷究物理。见得通透。又于日用。早晏持守。无论巨细。一以实心应副。则用力之极。自然诚敬坚固。设有死生不测之祸。自能委命于天而顺受其正矣。不然一时慷慨杀身。则容或有之。而其于祸变。从容就义。有如伊川则未必能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答卢德济]
朱书每以良心断言明德者。盖只言心则虚灵而已。义理不足观。只言性则理而已。不能有所主宰故耶。(德济)
朱子于中庸序。有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而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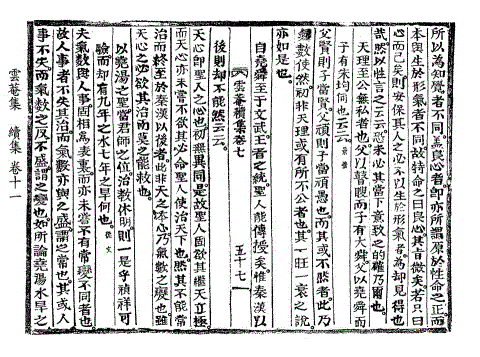 所以为知觉者不同。盖良心者。即亦所谓原于性命之正。而本与生于形气者不同。故特命之曰良心。其旨微矣。若只曰心而已矣。则安保其人之必不以生于形气者。为却见得也哉。然以性言之云云。恐未必其当下意致之的确乃尔也。
所以为知觉者不同。盖良心者。即亦所谓原于性命之正。而本与生于形气者不同。故特命之曰良心。其旨微矣。若只曰心而已矣。则安保其人之必不以生于形气者。为却见得也哉。然以性言之云云。恐未必其当下意致之的确乃尔也。[答俞景善(二条)]
天理至公无私者也。父以瞽瞍而子有大舜。父以尧舜而子有朱均何也云云。(景善)
父贤则子当贤。父顽则子当顽愚也。而其或不然者。此乃气数使然。初非天理或有所不公者也。其一旺一衰之说。亦如是也。
自尧舜至于文武。王者之统。圣人能传授矣。惟秦汉以后则却不能然云云。
天心即圣人之心也。初无异同。是故圣人固欲其继天立极。而天心亦未尝不欲其必命圣人使治天下也。然其不能常治而终至于秦汉以后者。此非天之本心。乃气数之变也。虽天心之必欲其治而莫之能救也。
[答卢德文(二条)]
以尧汤之圣。当君师之位。治教休明。则一是乎祯祥可验。而却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何也。(德文)
夫气数与人事。固相为表里。而亦未尝不有常变不同者也。故人事者不失其治。而气数亦与之盛。谓之常也。其或人事不失。而气数之反不盛。谓之变也。如所论尧汤水旱之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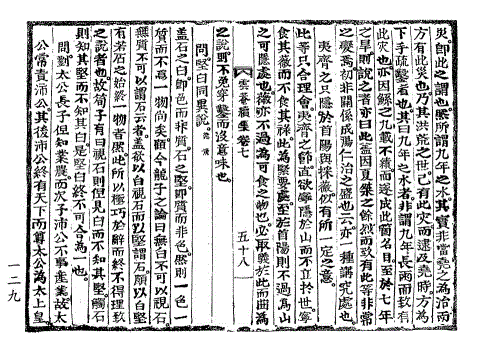 灾。即此之谓也。然所谓九年之水。其实非当尧之为治而方有此灾也。乃其洪荒之世。已有此灾。而逮及尧时。方为下手疏凿者也。其曰九年之水者。非谓九年长雨而致有此灾也。亦因鲧之九载不绩。而遂成此个名目。至于七年之旱。则说之者亦曰此盖因夏桀之馀烈而致有此等非常之变焉。初非关系成汤仁治之盛也云。亦一种讲究处也。
灾。即此之谓也。然所谓九年之水。其实非当尧之为治而方有此灾也。乃其洪荒之世。已有此灾。而逮及尧时。方为下手疏凿者也。其曰九年之水者。非谓九年长雨而致有此灾也。亦因鲧之九载不绩。而遂成此个名目。至于七年之旱。则说之者亦曰此盖因夏桀之馀烈而致有此等非常之变焉。初非关系成汤仁治之盛也云。亦一种讲究处也。夷齐之只隐于首阳与采薇。似有所一定之意。
此等只合理会。夷齐之节。直欲宁隐于山而不立于世。宁食其薇而不食其禄。此为紧要处。至于首阳则不过为山之可隐处也。薇亦不过为可食之物也。必取义于此而曲为之说。则不免穿凿而没意味也。
[答卢德济]
问。坚白同异说。(德济)
盖石之白。即色而非质。石之坚。即质而非色。然则一色一质而不为一物尚矣。顾今龙子之论曰无白不可以视石。无质不可以谓石云者。盖欲以白视石而以坚谓石。颇以白坚有若石之始终一物者然。此所以极巧于辞而终不得理致之说者也。故笋子有曰视石则但见白而不知其坚。触石则知其坚而不知其白。是坚白终不可合为一也。
[答崔洛九]
问。刘太公长子但知业农。而次子沛公不事产业。故太公常责沛公。其后沛公终有天下而尊太公为太上皇。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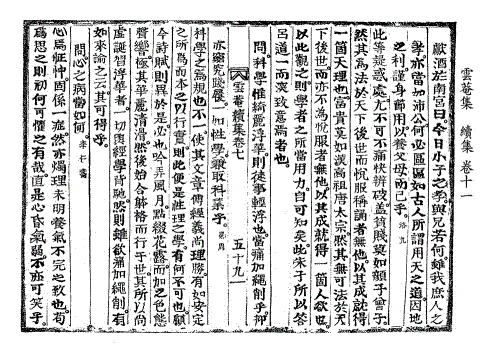 献酒于南宫曰。今日小子之孝。与兄若何。虽我庶人之孝。亦当如沛公。何必区区如古人所谓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而已乎。(洛九)
献酒于南宫曰。今日小子之孝。与兄若何。虽我庶人之孝。亦当如沛公。何必区区如古人所谓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而已乎。(洛九)此等疑惑处。尤不可不痛快辨破。盖贫贱莫如颜子曾子。然其为法于天下后世而悦服称诵者无他。以其成就得一个天理也。富贵莫如汉高祖唐太宗。然其无可法于天下后世。而亦不为悦服者无他。以其成就得一个人欲也。以此观之。则学者之所当用力。自可知矣。此朱子所以答吕道一而深致意焉者也。
[答金冕周]
问。科学惟绮丽浮华。则徒事轻浮也。当痛加绳削乎。抑亦穷究践履。一如性学。兼取科业乎。(冕周)
科学之为规也不一。使其文章传经义尚理胜。有如安定之所为而本之以行实。则此便是性理之学。有何不可也。顾今诗赋则异于是。必也吟弄风月。点缀花露。而加之色态声响。极其华丽清滑。然后始合体格而行于世。其所以尚虚诞习浮华者。一切与经学背驰。然则虽欲痛加绳削。有如来谕之云。其可得乎。
[答李仁寿(十三条)]
问。心之病当如何。(李仁寿)
心焉怔忡。固系一症。然亦烛理未明养气不完之致也。苟为思之则初何可惧之有哉。直是心昏气弱。不亦可笑乎。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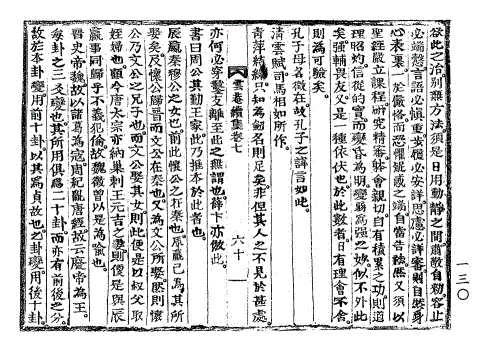 欲此之治。别无方法。须是日用动静之间。肃敬自敕。容止必端悫。言语必慎重。步履必安详。思虑必详审。则自然身心表里。一于俨恪。而恐惧疑惑之端。自当告袪。然又须以圣经严立课程。研究精审。体会亲切。自有积累之功。则道理昭灼。信从的实。而变昏为明。变弱为强之妙。似不外此矣。强辅畏友。又是一种依伏也。于此数者。日有理会不舍。则为可验矣。
欲此之治。别无方法。须是日用动静之间。肃敬自敕。容止必端悫。言语必慎重。步履必安详。思虑必详审。则自然身心表里。一于俨恪。而恐惧疑惑之端。自当告袪。然又须以圣经严立课程。研究精审。体会亲切。自有积累之功。则道理昭灼。信从的实。而变昏为明。变弱为强之妙。似不外此矣。强辅畏友。又是一种依伏也。于此数者。日有理会不舍。则为可验矣。孔子母名徵在。故孔子之讳言如此。
清云赋。司马相如所作。
青萍结绿。只知为剑名则足矣。非但其人之不见于甚处。亦何必穿凿支离至此之无谓也。薛卞亦仿此。
书曰周公其勤王家。此乃推本于此者也。
辰嬴秦穆公之女也。前此怀公之在秦也。辰羸已为其所娶矣。及怀公归晋而文公在秦也。又为文公所娶。然则怀公乃文公之兄子也。而文公娶其女。则此便是以叔父取侄妇也。顾今唐太宗亦纳巢剌王元吉之妻。则便是与辰嬴事同归乎不义犯伦。故魏徵曾以是为喻也。
晋史帝魏。故以诸葛为寇。周纪乱唐经。故云废帝为王。
每卦之三爻变也。其所用俱为二十卦。而亦有前后之分。故于本卦变。用前十卦。以其为贞故也。之卦变。用后十卦。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1H 页
 以其为悔故也。
以其为悔故也。一度里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事见造化论。
半强之强。犹言胜也。不可以里数言。月远为夜。盖亦捞摸之说。而疏阔不近于事情。故先儒不以为然也。夏至之日。视春秋愈向北。春秋之日。视冬至愈向北。故去极有远近也。九道之青黄赤白黑。不过取其本方色以定其四时之行而已也。日月行自有程界。不与二十八宿相为进退。岂可以二十八宿形容其道里之次乎。
日月蚀预测。以其本月内日月行次之近远知之也。
启明星之或见或否。非有隐见。乃以其近日远日。仍有或见或否之不同也。
婺星。乃六十年始一周之星也。
[答崔洛九(二条)]
问。格致章间尝二字之义。(崔洛九)
迫于来问之煎逼。不得不剖析(剖析之义。已见卢德圭问目。)碎裂。要有以准备。间尝下字之义而已矣。而其意味则浅薄甚矣。此既非本义之所系。又未必本义之的尔也。则恐不须剖析太甚。自取韩公虫鱼之诮。却是活略看取。必以发语之辞归之。有如曰若稽古三月之越若来。初无意义之可论而实为语辞之妙方。古人之文。往往未尝不有此等之例也。而况朱子之书。例多有盖尝论之窃尝论之之等语。以此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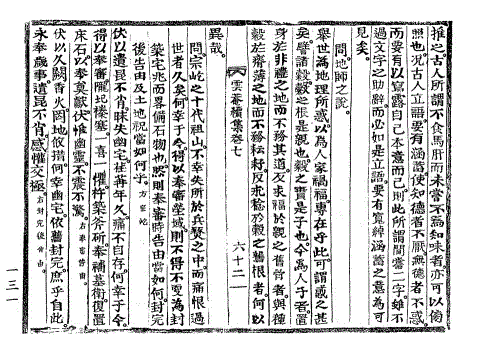 推之。古人所谓不食马肝而未尝不为知味者。亦可以傍照也。况古人立语。要有涵蓄。使知德者不厌。无德者不惑。而要有以写露自己本意而已。则此所谓间尝二字。虽不过文字之助辞。而必如是立语。要有宽绰涵蓄之意为可见矣。
推之。古人所谓不食马肝而未尝不为知味者。亦可以傍照也。况古人立语。要有涵蓄。使知德者不厌。无德者不惑。而要有以写露自己本意而已。则此所谓间尝二字。虽不过文字之助辞。而必如是立语。要有宽绰涵蓄之意为可见矣。问。地师之说。
举世为地理所惑。以为人家祸福。专在乎此。可谓惑之甚矣。譬诸谷。谷之根是亲也。谷之实是子也。今为人子者。置身于非礼之地而不务其道。反求福于亲之旧骨者。与种谷于瘠薄之地而不务耘耔。反求稔于谷之旧根者。何以异哉。
[答方宗屹(三条)]
问。宗屹之十代祖山。不幸失所于兵燹之中。而痛恨过世者久矣。何幸于今。得以奉审茔域。则不得不更为封筑宅兆而略备石物也。然则奉审时告由当如何。封完后告由及土地祝当如何乎。(方宗屹)
伏以遗昆不肖。昧失幽宅。荏苒年久。痛不自存。何幸于今。得以奉审。陇圮榛塞。一喜一惧。杵筑斧斫。奉补墓卫。复置床石。以奉奠献。伏惟幽灵。不震不惊。(右奉审告由。)
伏以久阙香火。罔地攸措。何幸幽宅。依旧封完。庶乎自此。永奉岁事。遗昆不肖。感欢交极。(右封完后告由。)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2H 页
 昧失先墓。痛不自已。今始奉审。复庸修筑。惟神保佑。俾无后艰。(右土地祝文。)
昧失先墓。痛不自已。今始奉审。复庸修筑。惟神保佑。俾无后艰。(右土地祝文。)[答卢德圭]
问。所命日记。初甚易之。及其随录。辞益不达。至如书札。本儒者事。然亦生疏。终难成说何如。敢请修润。(德圭)
文多不能尽览。然此段所著。逐一结绝。鞭辟向里者。足以字娓句呈矣。以故排铺之地。或不免有苦心极力之意。幸于日用工夫。要须宽以居之。虚以待之。要得为大施为。极充扩之渐。则似好也耳。非但日记一事为然也。
修润卢德圭书
[答桂亚常]
居常慕仰。不以无雅有间。不意昨者。令似惠肯本斋。日夕讲磨。聚会密迩。其于快偿夙私。已觉区区。又见其德性纯勤。工夫质悫。虽造次间。旋旋收拾。不或有失。随众趱程。切切然欲听讲论而不欲但已者。在流辈罕有其比。如愚不敏。只是望洋缩气而已。却于日昨。遽发省行。故不免有所疑虑者。以为此友外虽勉励。内实未稳。故遽此告归。则其所以践约复会。殆不可以十分完璧矣。诚不自意其往复神速。若是其晷刻不差而出人意表也。然则志学之笃。跌扑不破而不容复疑也。但得鲤诲终始坚实。逐旋资送。不令间断而已。则成就之美。保必立俟矣。不必别作一道理。有以求益之也。伏承先施。致
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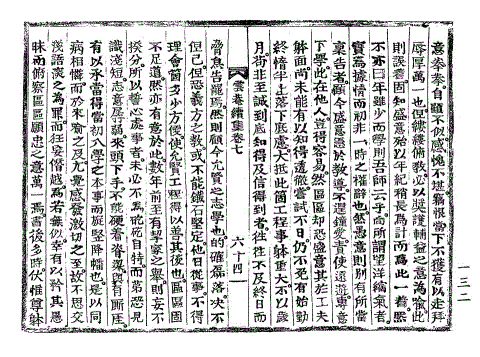 意拳拳。自顾不似。感愧不堪。窃恨当下不获有以走拜辱厚万一也。但缕缕俯教。必以奖护辅益之意为喻。此则误着。固知盛意殆以年纪稍长为计而为此一着。然不亦曰年虽少而学则吾师云乎。向所谓望洋缩气者。实为据情而初非一时之权辞也。然愚意则别有所当禀告者。顾今盛意急于教导。不遑钟爱。责使远游。专意下学。此在他人。岂得容易。然区区却恐盛意其于工夫体面。尚未能有以知得透彻。尝试不日。仍不免有始勤终惰半上落下底虑。大抵此个工程事体重大。不以岁月。苟非至诚到底知得及信得到者。往往不及终日而胁息告罢焉。然则顾今允贤之志学也。的确磊落。决不但已。但恐义方之教。或不能铁石坚定。他日从事。不得理会个多少方便。使允贤工程得以善其后也。区区固不足道。然亦有意于此。数年前至有挈家之举。则妄不揆分。所以誓心处事者。未必不为矻矻自特。而第恐见识浅短。志意孱弱。来头下手。不能硬着脊梁。与有厮厓。有以承当得当初入学之本事而旋竖降幡也。是以同病相怜。而于来喻之及。尤觉感发激切之至。故不思交浅语深之为罪。而狂妄僭越。为若无似。幸有以矜其愚昧而俯察区区愿忠之意万一焉。书后多时。伏惟尊体
意拳拳。自顾不似。感愧不堪。窃恨当下不获有以走拜辱厚万一也。但缕缕俯教。必以奖护辅益之意为喻。此则误着。固知盛意殆以年纪稍长为计而为此一着。然不亦曰年虽少而学则吾师云乎。向所谓望洋缩气者。实为据情而初非一时之权辞也。然愚意则别有所当禀告者。顾今盛意急于教导。不遑钟爱。责使远游。专意下学。此在他人。岂得容易。然区区却恐盛意其于工夫体面。尚未能有以知得透彻。尝试不日。仍不免有始勤终惰半上落下底虑。大抵此个工程事体重大。不以岁月。苟非至诚到底知得及信得到者。往往不及终日而胁息告罢焉。然则顾今允贤之志学也。的确磊落。决不但已。但恐义方之教。或不能铁石坚定。他日从事。不得理会个多少方便。使允贤工程得以善其后也。区区固不足道。然亦有意于此。数年前至有挈家之举。则妄不揆分。所以誓心处事者。未必不为矻矻自特。而第恐见识浅短。志意孱弱。来头下手。不能硬着脊梁。与有厮厓。有以承当得当初入学之本事而旋竖降幡也。是以同病相怜。而于来喻之及。尤觉感发激切之至。故不思交浅语深之为罪。而狂妄僭越。为若无似。幸有以矜其愚昧而俯察区区愿忠之意万一焉。书后多时。伏惟尊体云庵续集卷之十一 第 133H 页
 百福。萱堂万安。既仰且祝。靡日不挚。德圭仁庇。得以依省稔荷。三馀之业。年迈业退。初不足以向人说话也。(答桂亚常。)
百福。萱堂万安。既仰且祝。靡日不挚。德圭仁庇。得以依省稔荷。三馀之业。年迈业退。初不足以向人说话也。(答桂亚常。)[与金鍊书]
德圭昨自夏月。来接云斋。初非讲究为意。只为督儿劝课而已。不谓一日二日。耳闻目见。不外于是。其于观感。不无分数。而抑亦宿症。一切见却而不容复作。是则为幸。然此安知非一时偶尔之事。而亦岂可保来者之必不然也。故不敢妄说以致不扪之咎。然窃念禀质极弱。自幼至今。未尝一日无药者也。以一岁计之。净然稳过者。不曾有几个日矣。来此以后于今数朔。不复素祟有所告发于此焉。此未知何故欤。私自见惑。不审其端者也。所以尚此蹲留。随众托名而已。岂望有一毫见进也哉。但得所祟缘此告却。不复有作。则岂不为贱状之一幸乎。(与金鍊书。)
[答李仁寿(四条)]
问云云。(答李仁寿。)
剑所带之剑。履所着之履也。
厥父厥子之说。此乃譬喻其不可不终前人之事之谓也。注说分明。复何他问。
坼胄方欲害朱子。故乡人谋利者如是也。
六月僧。岂结夏之谓邪。去头绝尾。只行此句者。无乃有近于暗中出拳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