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竹圃集卷之九 第 x 页
竹圃集卷之九
杂著
杂著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1H 页
 读三国志
读三国志荀攸之赞。不知出于何人。而其曰德可配颜渊者。是何语也。颜渊何如人。而以荀攸比之耶。攸以朗陵之孙。为操谋士。已为见识之不明。而操之平生。多残暴不仁。如弑母后鸩皇子。其他枉杀忠良。虐流生灵。即其一生伎俩。而攸一不能谏止。德之一字。何可加于攸之身上。而且曰配颜渊云者。何所据之言耶。作此诗者。胸中全无分介。多见其不知量也。
祢衡之骂曹操。快则快矣。且可见衡之不畏疆御。疾恶如雠之意也。然而窃为衡不取也。操之为人何如。而欲直口面骂耶。衡若一骂而操能改心易虑则可矣。如吉平之谋泄而既死之势则骂之可矣。如刘先主之临阵朗诵衣带诏之时则亦可矣。无此数者。而以白面一书生。极口诟骂于当时大丞相。此岂非取祸之道耶。操以奸雄也。故不欲得杀贤之名。故使于刘表。表其能容物者耶。狼毒如黄祖。亦当据理就事论事而已。终至触犯其怒。乃殒其身。衡之一死。上不得成仁之美。下不得保身之机。虽谓之徒死可也。孔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1L 页
 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申屠蟠之韬晦。郭林宗之不为危言激论。先儒皆以明哲保身目焉。以是论之。衡之事不无遗憾焉。
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申屠蟠之韬晦。郭林宗之不为危言激论。先儒皆以明哲保身目焉。以是论之。衡之事不无遗憾焉。曹操之为人。或有人知渠之意则大忌之。操之心已无汉久矣。祢衡一见而以常怀篡逆畅骂之。操于此时。必冷汗遍体矣。操之不敢及其身篡汉。安知不由于衡之一骂耶。如衡者可谓颓波之砥柱。其凛凛之气。烈烈之声。如闻纸上。亦可谓死不死矣。如荀彧,陈群,杨修,王粲,钟繇,华歆,王朗之辈。以汉朝华裔名流中人。皆奴颜婢膝。助操为恶。或有不得其死者。或有苟图性命者。不免后世唾骂。彼胡为而为此哉。然则衡之骂操。非但骂操于当时。亦以骂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耳。
刘表之辞荆州于刘先主也。孔明劝之。关张亦劝之。而先主断意不受者。人皆谓失机。而愚独服先主之高见也。若受之于刘表生前。则一郡不可容二主。将何以处刘表耶。观于后来刘璋之事。可知矣。既不受之于生前。安能乘其丧而取之耶。此非仁德之主所可为也。或以为取之于刘琮降曹之时。则是取之于操。非取之于刘琮。似无不正矣。而曹操方驱数十万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2H 页
 雄兵。压境而来。虽有善谋之孔明。每事草创。何能猝定人心乎。刘表素无高智远虑。而以柔善抚众。众心必有不忘者矣。且有蔡瑁,张允,蔡中,蔡和辈符同蔡夫人刘琮。煽造蜚语。恐动民心。则内乱必作矣。其后西川之取。整顿有月。而无操兵之如是犯境。且未闻如蔡瑁辈从中煽乱。而犹有一日四五惊之事。况以荆襄要冲之地。其何能保其无事耶。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有淮夷三监之乱。先主看得此义欤。
雄兵。压境而来。虽有善谋之孔明。每事草创。何能猝定人心乎。刘表素无高智远虑。而以柔善抚众。众心必有不忘者矣。且有蔡瑁,张允,蔡中,蔡和辈符同蔡夫人刘琮。煽造蜚语。恐动民心。则内乱必作矣。其后西川之取。整顿有月。而无操兵之如是犯境。且未闻如蔡瑁辈从中煽乱。而犹有一日四五惊之事。况以荆襄要冲之地。其何能保其无事耶。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有淮夷三监之乱。先主看得此义欤。孙策之杀于吉。解之者以英雄伏妖许之。而窃疑策亦是短处也。吉之在江东别无造讹盗米之事。但有施符救病之方。则与张角,张鲁辈迥异矣。或虑其滋蔓则吉在东吴数十年。无一徒党。如策之心腹张昭辈皆敬奉焉。此无可虑者。目下能雨能晴之术。虽曰天道之适然。亦岂非神异乎。自古祈雨祈晴。在在史牒。其可尽归于诞妄耶。如吉辈以方外狂士。置之不问。如刘先主之处青城老叟可也。何至于必杀乃已耶。人谓策之死由于许贡之客。而其丧神憔形。未必不由于吉之作怪。则策之死以吉为祟亦可也。想策之为人。恃强矜愎。少容物之意。故曹操青梅煮酒之时。以策不列于英雄之目。郭嘉曰必死于小人之手。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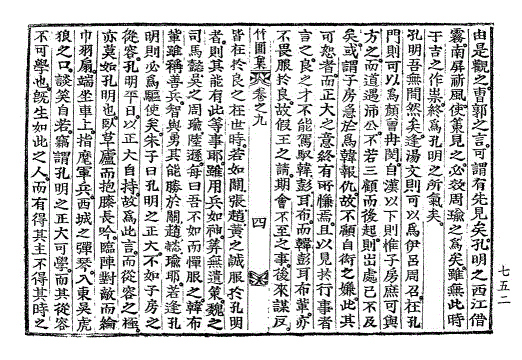 由是观之。曹郭之言。可谓有先见矣。孔明之西江借雾。南屏祈风。使策见之。必效周瑜之为矣。虽无此时于吉之作祟。终为孔明之所气矣。
由是观之。曹郭之言。可谓有先见矣。孔明之西江借雾。南屏祈风。使策见之。必效周瑜之为矣。虽无此时于吉之作祟。终为孔明之所气矣。孔明吾无间然矣。逢汤文则可以为伊吕周召。在孔门则可以为颜曾冉闵。自汉以下则惟子房庶可与方之。而道遇沛公。不若三顾而后起。则出处已不及矣。或谓子房急于为韩报仇。故不顾自衒之嫌。此其可恕者。而正大之意终有所慊焉。且以见于行事者言之。良之才不能驾驭韩,彭,耳,布。而韩彭耳布辈。亦不畏服于良。故假王之请。期会不至之事。后来谋反。皆在于良之在世时。若如关,张,赵,黄之诚服于孔明者。则其能有此等事耶。虽用兵如神。算无遗策。魏之司马懿,吴之周瑜,陆逊。每曰吾不如而惮服之。韩布辈虽称善兵。智与勇其能胜于关,赵,懿,瑜耶。若逢孔明则必为驱使矣。朱子曰孔明之正大。不如子房之从容。孔明平日。以正大自持。故为此言。而从容之极。亦莫如孔明也。卧草庐而抱膝长吟。临阵对敌而纶巾羽扇。端坐车上。指麾军兵。西城之弹琴。入东吴虎狼之口。谈笑自若。窃谓孔明之正大可学。而其从容不可学也。既生如此之人。而有得其主不得其时之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3H 页
 叹何哉。吾亦欲问天而已。
叹何哉。吾亦欲问天而已。伏龙,凤雏。论之者皆对举而言。疑若士元之才与孔明相埒。而实则士元之才。不知落下几层也。方统之献连环计。识破三气。则诚智谋有馀。而及其归汉。虽不自我求得。带他人书而来者。较之于三顾。不啻天渊。取蜀行军。动多掣肘。涪城之欲杀刘璋。是岂仁者之心乎。若无先主之禁止。则必得不义之名矣。如正大光明鞠躬尽瘁孔明之心。反疑之终有落凤坡之事。此则学问之未精。志虑之未纯。功名适足以累其心也。以是观之。统之见识。在徐庶之下。而使周瑜,司马懿闻之。岂不为所笑耶。无乃大数当前。天蔽其衷而然邪。
周公瑾于赤壁之役。排众议决策。遂使孟德破胆。开拓荆州。驾驭江东。群才任使有方。诚一代之人杰也。然而细究其始终。则不可以智谋有馀。为军师者名。尽乎局量偏浅。粗暴愚妄之一勇悍夫耳。掌中之书火字。虽与孔明同。而孔明则已知有东南风。公瑾则初未能料知。严冬之时。安能火攻北船耶。周瑜之书火字。有知觉耶。无知觉耶。何等智谋耶。方孔明之西江借箭。牢囚工匠。是何黄口辈之见识。南屏祈风。发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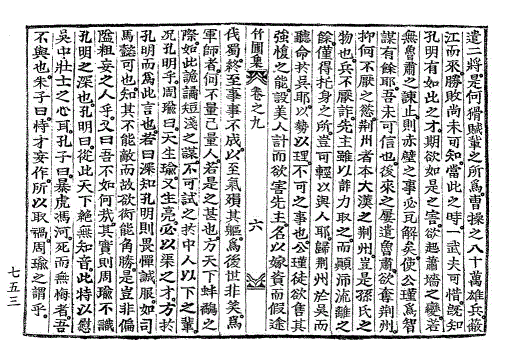 遣二将。是何猾贼辈之所为。曹操之八十万雄兵。蔽江而来。胜败尚未可知。当此之时。一武夫可惜。既知孔明有如此之才。期欲如是之害。欲起萧墙之变。若无鲁肃之谏止。则赤壁之事必瓦解矣。使公瑾为智谋有馀耶。吾未可信也。后来之屡遣鲁肃。欲夺荆州。抑何不厌之欲。荆州者本大汉之荆州。岂是孙氏之物也。兵不厌诈。先主虽以诈力取之。而颠沛流离之馀。仅得托身之所。岂可轻以与人耶。归荆州于吴而听命于吴耶。以势以理。不可之事也。公瑾徒欲售其强愎之能。设美人计而欲害先主。名以嫁资而假途伐蜀。终至事事不成。以至气殒其躯。为后世非笑。为军师者。何不量己量人。若是之甚也。方天下蚌鹬之际。如此诡谲短浅之谋。不可试之于中人以下之辈。况孔明乎。周瑜曰。天生瑜。又生亮。必以渠之才。方于孔明而为此言也。若曰深知孔明则畏惮诚服。如司马懿可也。知其不能敌而故欲衒能角胜。是岂非偏隘粗妄之人乎。又曰吾不如何哉。其实则周瑜不识孔明之深也。孔明曰。从此天下绝无知音。此特以慰吴中壮士之心耳。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朱子曰。恃才妄作。所以取祸。周瑜之谓乎。
遣二将。是何猾贼辈之所为。曹操之八十万雄兵。蔽江而来。胜败尚未可知。当此之时。一武夫可惜。既知孔明有如此之才。期欲如是之害。欲起萧墙之变。若无鲁肃之谏止。则赤壁之事必瓦解矣。使公瑾为智谋有馀耶。吾未可信也。后来之屡遣鲁肃。欲夺荆州。抑何不厌之欲。荆州者本大汉之荆州。岂是孙氏之物也。兵不厌诈。先主虽以诈力取之。而颠沛流离之馀。仅得托身之所。岂可轻以与人耶。归荆州于吴而听命于吴耶。以势以理。不可之事也。公瑾徒欲售其强愎之能。设美人计而欲害先主。名以嫁资而假途伐蜀。终至事事不成。以至气殒其躯。为后世非笑。为军师者。何不量己量人。若是之甚也。方天下蚌鹬之际。如此诡谲短浅之谋。不可试之于中人以下之辈。况孔明乎。周瑜曰。天生瑜。又生亮。必以渠之才。方于孔明而为此言也。若曰深知孔明则畏惮诚服。如司马懿可也。知其不能敌而故欲衒能角胜。是岂非偏隘粗妄之人乎。又曰吾不如何哉。其实则周瑜不识孔明之深也。孔明曰。从此天下绝无知音。此特以慰吴中壮士之心耳。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朱子曰。恃才妄作。所以取祸。周瑜之谓乎。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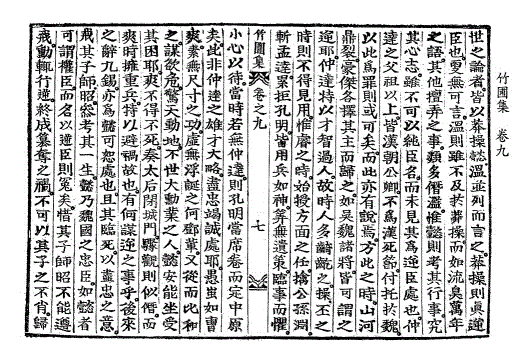 世之论者。皆以莽操懿,温并列而言之。莽操则真逆臣也。更无可言。温则虽不及于莽操。而如流臭万年之语。其他擅弄之事。类多僭滥。惟懿则考其行事。究其心志。虽不可以纯臣名。而未见其为逆臣处也。仲达之父祖以上。皆汉朝公卿。不为汉死节。付托于魏。以此为罪则或可矣。而此亦有说焉。方此之时。山河鼎裂。豪杰各择其主而归之。如吴魏诸将。皆可谓之逆耶。仲达特以才智过人。故时人多齮龁之。操,丕之时则不得见用。惟睿之时。始授方面之任。擒公孙渊。斩孟达。累拒孔明。皆用兵如神。算无遗策。临事而惧。小心以待。当时若无仲达。则孔明当席卷而定中原矣。此非仲达之雄才大略。尽忠竭诚处耶。愚蚩如曹爽。素无尺寸之功。虚无浮诞之何邓辈。又从而比和之。谋欲危。惊天动地。不世大勋业之人。懿安能坐受其困耶。爽不得不死。奏太后闭城门。骤观则似僭。而爽时拥重兵。特以避祸故也。有何谋逆之事乎。后来之辞九锡。亦为懿可恕处也。且其临死。以尽忠之意。戒其子师,昭。参考其一生。懿乃魏国之忠臣。如懿者可谓权臣。而名以逆臣则冤矣。惜其子师昭不能遵戒。动辄行逆。终成篡夺之祸。不可以其子之不肖。归
世之论者。皆以莽操懿,温并列而言之。莽操则真逆臣也。更无可言。温则虽不及于莽操。而如流臭万年之语。其他擅弄之事。类多僭滥。惟懿则考其行事。究其心志。虽不可以纯臣名。而未见其为逆臣处也。仲达之父祖以上。皆汉朝公卿。不为汉死节。付托于魏。以此为罪则或可矣。而此亦有说焉。方此之时。山河鼎裂。豪杰各择其主而归之。如吴魏诸将。皆可谓之逆耶。仲达特以才智过人。故时人多齮龁之。操,丕之时则不得见用。惟睿之时。始授方面之任。擒公孙渊。斩孟达。累拒孔明。皆用兵如神。算无遗策。临事而惧。小心以待。当时若无仲达。则孔明当席卷而定中原矣。此非仲达之雄才大略。尽忠竭诚处耶。愚蚩如曹爽。素无尺寸之功。虚无浮诞之何邓辈。又从而比和之。谋欲危。惊天动地。不世大勋业之人。懿安能坐受其困耶。爽不得不死。奏太后闭城门。骤观则似僭。而爽时拥重兵。特以避祸故也。有何谋逆之事乎。后来之辞九锡。亦为懿可恕处也。且其临死。以尽忠之意。戒其子师,昭。参考其一生。懿乃魏国之忠臣。如懿者可谓权臣。而名以逆臣则冤矣。惜其子师昭不能遵戒。动辄行逆。终成篡夺之祸。不可以其子之不肖。归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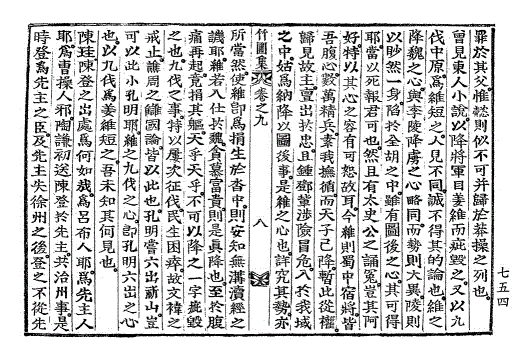 罪于其父。惟懿则似不可并归于莽操之列也。
罪于其父。惟懿则似不可并归于莽操之列也。曾见东人小说。以降将军目姜维而疵毁之。又以九伐中原。为维短之。人见不同。诚不得其的论也。维之降魏之心。与李陵降虏之心略同。而势则大异。陵则以眇然一身。陷于全胡之中。虽有图后之心。其可得耶。当以死报君可也。然且有太史公之诵冤。岂其阿好。特以其心之容有可恕故耳。今维则蜀中宿将。皆吾腹心。数万精兵。素我抚循。而天子已降。暂此从权。归见故主。亶出于忠。且钟邓辈涉险冒危。入于我域之中。姑为纳降以图后事。是维之心也。详究其势。亦所当然。使维即为捐生于沓中。则安知无沟渎经之讥耶。维若入仕于魏。贪慕富贵。则是真降也。至于腹痛再起。竟捐其躯。天乎天乎。不可以降之一字疵毁之也。九伐之事。特以屡次征伐。民生困瘁。故文袆之戒止。谯周之雠国论。皆以此也。孔明尝六出祈山。岂可以此小孔明耶。维之九伐之心。即孔明六出之心也。以九伐为姜维短之。吾未知其何见也。
陈圭,陈登之出处为何如哉。为吕布人耶。为先主人耶。为曹操人邪。陶谦初送陈登于先主。共治州事。是时登为先主之臣。及先主失徐州之后。登之不从先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5H 页
 主何也。吕布之据徐州。登为布使。往来于曹操。想必是时登为布之幕宾明矣。为人幕宾。终始内诅外
主何也。吕布之据徐州。登为布使。往来于曹操。想必是时登为布之幕宾明矣。为人幕宾。终始内诅外田丰,沮授。诚一代之良才也。袁绍之无能为。必无不知之理。而矢死不去者何也。袁氏四世三公。门多故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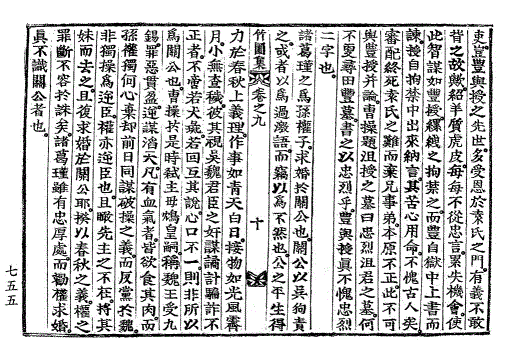 吏。岂礼与授之先世。多受恩于袁氏之门。有义不敢背之故欤。绍羊质虎皮。每每不从忠言。累失机会。使此智谋如丰授。缧绁之拘禁之。而礼自狱中上书而谏。授自拘禁中出来纳言。其苦心用命。不愧古人矣。审配终死袁氏之难而弃兄事弟。本原不正。此不可与礼授并论。曹操题沮授之墓曰忠烈沮君之墓。何不更寻田丰墓。书之以忠烈乎。礼与授真不愧忠烈二字也。
吏。岂礼与授之先世。多受恩于袁氏之门。有义不敢背之故欤。绍羊质虎皮。每每不从忠言。累失机会。使此智谋如丰授。缧绁之拘禁之。而礼自狱中上书而谏。授自拘禁中出来纳言。其苦心用命。不愧古人矣。审配终死袁氏之难而弃兄事弟。本原不正。此不可与礼授并论。曹操题沮授之墓曰忠烈沮君之墓。何不更寻田丰墓。书之以忠烈乎。礼与授真不愧忠烈二字也。诸葛瑾之为孙权子。求婚于关公也。关公以吴狗责之。或者以为过激语。而窃以为不然也。公之平生得力于春秋上义理。作事如青天白日。接物如光风霁月。小无查秽。彼其视吴魏君臣之奸谋谲计骗诈不正者。不啻若犬彘。若回互其说。心口不一。则非所以为关公也。曹操于是时弑主母鸩皇嗣。称魏王受九锡。罪恶贯盈。逆谋滔天。凡有血气者。皆欲食其肉。而孙权独何心弃却前日同谋破操之义。而反党于魏。非独操为逆臣。权亦逆臣也。且瞰先主之不在。将其妹而去之。且复求婚于关公耶。揆以春秋之义。权之罪断不容于诛矣。诸葛瑾虽有忠厚处。而劝权求婚。真不识关公者也。
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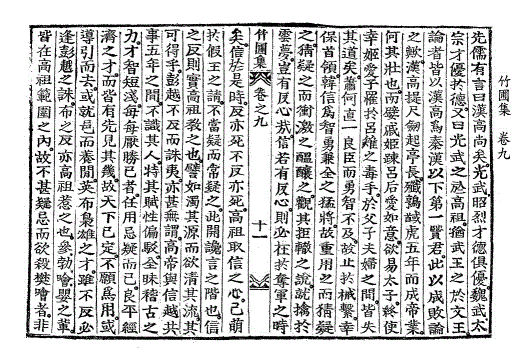 先儒有言曰汉高尚矣。光武,昭烈才德俱优。魏武,太宗才优于德。又曰光武之于高祖。犹武王之于文王。论者皆以汉高为秦汉以下第一贤君。此以成败论之欤。汉高提尺剑起亭长。歼鹑馘虎五年而成帝业。何其壮也。而嬖戚姬疏吕后爱如意。欲易太子。终使幸姬爱子罹于吕雉之毒手。于父子夫妇之间。皆失其道矣。萧何直一良臣而勇智不及。故止于械系。幸保首领。韩信为智勇兼全之猛将。故重用之而猜疑之。猜疑之而冲激之酝酿之。观其拒辙之说。就擒于云梦。岂有反心哉。信若有反心。则必在于夺军之时矣。信于是时。反亦死不反亦死。高祖取信之心。已萌于假王之请。不当疑而常疑之。此开谗言之阶也。信之反则实高祖教之也。譬如浊其源而欲清其流。其可得乎。彭越不反而诛夷。亦甚无谓。高帝与信越共事五年之间。不识其人。特其赋性偏驳。全昧稽古之力。才智短浅。每每厌胜己者。任用忌疑而已。良平经济之才。而皆有先见其几。故天下已定。不愿为用。或导引而去。或就邑而养閒。英布枭雄之才。虽不反必逢彭越之诛。布之反亦高祖惹之也。参,勃,哙,婴之辈。皆在高祖范围之内。故不甚疑忌而欲杀樊哙者。非
先儒有言曰汉高尚矣。光武,昭烈才德俱优。魏武,太宗才优于德。又曰光武之于高祖。犹武王之于文王。论者皆以汉高为秦汉以下第一贤君。此以成败论之欤。汉高提尺剑起亭长。歼鹑馘虎五年而成帝业。何其壮也。而嬖戚姬疏吕后爱如意。欲易太子。终使幸姬爱子罹于吕雉之毒手。于父子夫妇之间。皆失其道矣。萧何直一良臣而勇智不及。故止于械系。幸保首领。韩信为智勇兼全之猛将。故重用之而猜疑之。猜疑之而冲激之酝酿之。观其拒辙之说。就擒于云梦。岂有反心哉。信若有反心。则必在于夺军之时矣。信于是时。反亦死不反亦死。高祖取信之心。已萌于假王之请。不当疑而常疑之。此开谗言之阶也。信之反则实高祖教之也。譬如浊其源而欲清其流。其可得乎。彭越不反而诛夷。亦甚无谓。高帝与信越共事五年之间。不识其人。特其赋性偏驳。全昧稽古之力。才智短浅。每每厌胜己者。任用忌疑而已。良平经济之才。而皆有先见其几。故天下已定。不愿为用。或导引而去。或就邑而养閒。英布枭雄之才。虽不反必逢彭越之诛。布之反亦高祖惹之也。参,勃,哙,婴之辈。皆在高祖范围之内。故不甚疑忌而欲杀樊哙者。非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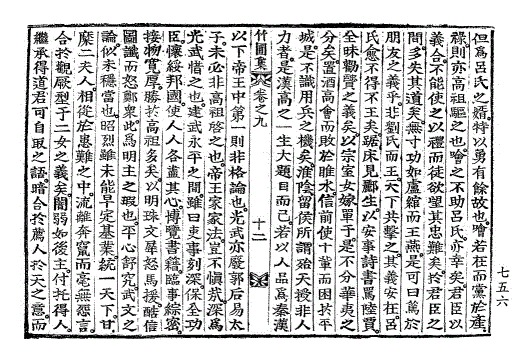 但为吕氏之婿。特以勇有馀故也。哙若在而党于产,禄。则亦高祖驱之也。哙之不助吕氏。亦幸矣。君臣以义合。不能使之以礼而徒欲望其忠难矣。于君臣之间。多失其道矣。无寸功如卢绾而王燕。是可曰笃于朋友之义乎。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其义安在。吕氏愈不得不王矣。踞床见郦生。以安事诗书骂陆贾。全昧劝贤之义矣。以宗室女嫁单于。是不分华夷之分矣。置酒高会而败于睢水。信前使十辈而困于平城。是不识用兵之机矣。淮阴,留侯所谓殆天授非人力者。是汉高之一生大题目而已。若以人品为秦汉以下帝王中第一则非格论也。光武亦废郭后易太子。未必非高祖启之也。帝王家家法。岂不慎哉。深为光武惜之也。建武永平之间。虽曰吏事刻深。保全功臣。怀绥邦国。使人人各尽其心。博览书籍。临事综密。接物宽厚。胜于高祖多矣。以明珠文犀怒马援。酷信图谶而怒郑众。此为明主之瑕也。平心舒究。武文之论。似未稳当也。昭烈虽未能早定基业。统一天下。甘,糜二夫人。相从于患难之中。流离奔窜而毫无怨言。合于观厥型于二女之义矣。闇弱如后主。付托得人。继承得道君可自取之语。暗合于荐人于天之意。而
但为吕氏之婿。特以勇有馀故也。哙若在而党于产,禄。则亦高祖驱之也。哙之不助吕氏。亦幸矣。君臣以义合。不能使之以礼而徒欲望其忠难矣。于君臣之间。多失其道矣。无寸功如卢绾而王燕。是可曰笃于朋友之义乎。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其义安在。吕氏愈不得不王矣。踞床见郦生。以安事诗书骂陆贾。全昧劝贤之义矣。以宗室女嫁单于。是不分华夷之分矣。置酒高会而败于睢水。信前使十辈而困于平城。是不识用兵之机矣。淮阴,留侯所谓殆天授非人力者。是汉高之一生大题目而已。若以人品为秦汉以下帝王中第一则非格论也。光武亦废郭后易太子。未必非高祖启之也。帝王家家法。岂不慎哉。深为光武惜之也。建武永平之间。虽曰吏事刻深。保全功臣。怀绥邦国。使人人各尽其心。博览书籍。临事综密。接物宽厚。胜于高祖多矣。以明珠文犀怒马援。酷信图谶而怒郑众。此为明主之瑕也。平心舒究。武文之论。似未稳当也。昭烈虽未能早定基业。统一天下。甘,糜二夫人。相从于患难之中。流离奔窜而毫无怨言。合于观厥型于二女之义矣。闇弱如后主。付托得人。继承得道君可自取之语。暗合于荐人于天之意。而竹圃集卷之九 第 757H 页
 时异势殊。故特说以至诚无间。非有所强勉而发。与关张誓同生死而终践其言。三顾草庐而得鱼水之欢。师郑玄而得力。友卢植而救难。识赵云之不反。言马谡之误事。力斩黄巾。英才卓然。奉诏讨贼。大义昭揭。夫妇父子君臣之各尽其道。笃于兄弟。信于朋友。用兵之机。知人之明。比光武而犹胜。其视高祖。不啻珷玞之于良玉。当以昭烈为秦汉以下帝王中第一也。汉高尚矣之论。未知其然乎否也。奸猾如曹操。权诈如唐宗。已有定论。不必架叠焉。
时异势殊。故特说以至诚无间。非有所强勉而发。与关张誓同生死而终践其言。三顾草庐而得鱼水之欢。师郑玄而得力。友卢植而救难。识赵云之不反。言马谡之误事。力斩黄巾。英才卓然。奉诏讨贼。大义昭揭。夫妇父子君臣之各尽其道。笃于兄弟。信于朋友。用兵之机。知人之明。比光武而犹胜。其视高祖。不啻珷玞之于良玉。当以昭烈为秦汉以下帝王中第一也。汉高尚矣之论。未知其然乎否也。奸猾如曹操。权诈如唐宗。已有定论。不必架叠焉。赵人之欲使乐毅伐燕也。毅曰。畴昔事昭王。不从伐燕。以甘宁射杀黄祖之事较之。则毅乃不忠之徒欤。燕惠之不用乐毅。黄祖之不用甘宁同也。而毅乃如彼。宁独争先。射杀黄祖。宁可为忠耶。宁是忍人而贼心尚未祛也。既反归于东吴。当效忠之势而独效忠于射杀故主之地耶。宁使程普射之。宁何忍张弓逼前耶。庞德不思其故主与乃兄之在蜀。以杀嫂绝兄之事。畅言于曹操之前。敢与关公抗锋。是亦甘宁一类物也。吴魏诸将。类多如此。以关,张堂堂正正。义重如山之人观之。则安得不以狗也鼠也责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