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栎庵集卷之十二(晋山姜晋奎晋五著)
杂著
杂著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4H 页
 家训(镜湖录)凡二十八条
家训(镜湖录)凡二十八条行义必修。
行义者。人之所以为人也。人而无行义。则与禽兽奚择哉。为子而孝。为父而慈。为弟而顺。为兄而友。为臣而忠。为夫而义。为友而信。以至居处行动出入步趣威仪容色言语视听事上御下待人接物。无时无处无事无物。各有当行之义。修之则为人。反是则形虽人矣。名虽人矣。其实则非人也。可不戒哉。可不勉哉。此二十八条之总脑也。
文学必勤。
行义者。固人之所必修者。然必知之而后。可以行之。文也者。载此者也。学也者。效此者也。苟不就其所载而效之。则虽欲孝而不知所以为孝。虽欲忠而不知所以为忠。推此类之。莫不皆然。虽或以资质之美。有所暗合。不过为不践迹之善人而已。此大学之格物致知。所以居于正心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4L 页
 诚意修身齐家之先也。若夫寻章摘句。以资举业之工。贪多务广。以求博洽之誉。则非吾所谓文学也。
诚意修身齐家之先也。若夫寻章摘句。以资举业之工。贪多务广。以求博洽之誉。则非吾所谓文学也。礼法必遵。
礼者天理之节文。法者人为之禁防。礼所以约情。而法所以辅礼也。有纲领焉。有条目焉。有根本焉。有枝叶焉。必须正其纲而详其目。务其本而达其枝。则其斟酌损益。庶乎可以宜于今而不泥于古矣。大抵人自有生以后。则气为之主。故义理微而情欲胜。莫不乐放纵而恶拘检。喜恣肆而惮谨严。不有礼法以制饬之。则一转而为浮诞。再转而为猖狂。三转而为悖逆。以至辱名忝先丧身覆家者。真如下山之易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俭约必崇。
俭者不盈之谓。约者不放之谓。不盈则常保其盈。不放则常固其守。此自然之理也。假如十分之物。过一分则一分损。损而又损。则终至于无矣。不及一分则一分积。积而又积。则终至于盈矣。非独财产为然。天下万事。莫不皆然。是故以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5H 页
 多问于寡。以能问于不能。有若无。实若虚者。俭约于德也。战战兢兢。常若有鬼神之临父师之诏者。俭约于心也。谨慎谦拙。跬步之间。惟恐有失者。俭约于行也。退一步低一头。不以贤知先人。不以气势凌人者。俭约于世也。一衣一食。恒若过分者。俭约于财也。故俭则贫者恒有馀。约则愚人亦寡过矣。若夫俭而至于啬。约而至于迂。则非吾所谓俭约也。
多问于寡。以能问于不能。有若无。实若虚者。俭约于德也。战战兢兢。常若有鬼神之临父师之诏者。俭约于心也。谨慎谦拙。跬步之间。惟恐有失者。俭约于行也。退一步低一头。不以贤知先人。不以气势凌人者。俭约于世也。一衣一食。恒若过分者。俭约于财也。故俭则贫者恒有馀。约则愚人亦寡过矣。若夫俭而至于啬。约而至于迂。则非吾所谓俭约也。孝友必笃。
孝友者。百行之源也。自此而推则可以忠于君。可以睦于族。可以信于友。可以慈于众矣。夫天下之亲。莫亲于父母兄弟。岂本有不孝不友之人哉。特以人不知学而汩于利欲之私。以至丧其本性。而又或有顽父嚚母暴兄傲弟。先失其道。疑阻生于积渐。争阋仍成怨毒。一体分如路人。骨肉便成仇雠。可不痛哉。至哉言乎。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又曰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常常存得此心。则天下无不可孝之父母。无不可友之兄弟矣。若夫有至性深爱者。自然不见父母之非。而自然不相犹矣。又何待于立训以教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5L 页
 之也。
之也。奉先必诚。
奉先者。人道之大节也。生而致其养。死而致其哀。祭而致其享。此孝子顺孙之所以自尽其心也。可不诚乎。然世之人。或有尽力于养生送死。而于奉先之事则未免有忽之者。盖远则忘。久则怠。人情然也。夫以吾祖先所传之血气。萃彼祖先已散之精神。而欲来享之者。尤不可以不诚也。传曰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此之谓也。噫。有而啬之非诚也。无而丰之非诚也。修饰仪节非诚也。夸美观听非诚也。要使意先于物。情多于文。表里纯笃。幽明贯彻。则庶乎其可以享之矣。此以下就事而言之者也。
教子必严。
教子者。欲以传其家也。有子而不教。何以传祖先之业。此古人所谓至要莫如教子也。然世之人。多溺于爱。自幼便养成骄惰。到长益凶狠。此不严之过也。然吾之所谓严者。非谓如悍马之力加钳勒。坚木之㬥令摧折也。须自孩提之时。教以孝悌恭顺之道。纳之规矩绳墨之中。不使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6H 页
 有毫分放逸自肆。因以成习。则自然不畔于道。而设或有一时做错。渠已自知其非而无不受之诲矣。然此亦自吾身始。不然则有夫子未出之患矣。不可不先自勉也。
有毫分放逸自肆。因以成习。则自然不畔于道。而设或有一时做错。渠已自知其非而无不受之诲矣。然此亦自吾身始。不然则有夫子未出之患矣。不可不先自勉也。御下必宽。
宽者所以得众也。恤其饥寒。节其劳逸。此御仆之宽也。原其情察其心。不责其所不能。不强其所不欲。此御民之宽也。若烦碎苛刻。察察以为明。嗃嗃以为威。则纵平日以尊卑之等贵贱之分不敢抗。然其心则离矣。缓急何以得其力乎。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宁人欺我。无我欺人。此君子之用心。而尤切于御下之际。亦足为养后福之一道也。夫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所谓宽者固非废弛放纵之谓也。
接人必恭。
恭者德之聚也。天下之恶德非一。而莫甚于骄傲。天下之善行固多。而莫先于谦恭。彼无狭而自恃者。固不足言。或以势力骄人。或以货财骄人。或以阀阅骄人。或以才艺骄人。或以文学骄人。势力货财阀阅在外。失之则不能以骄。才艺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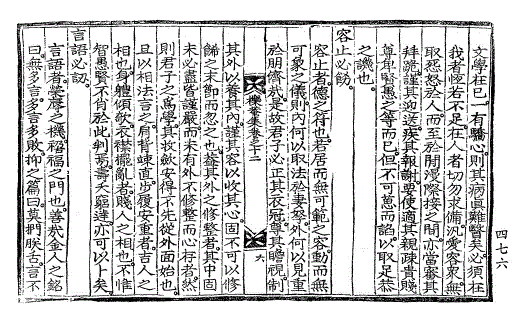 文学在己。一有骄心。则其病真难医矣。必须在我者恒若不足。在人者切勿求备。汎爱容众。无取怨怒于人。而至于閒漫际接之间。亦当审其拜跪。谨其迎送。疾其报谢。要使适其亲疏贵贱尊卑贤愚之等而已。但不可葸而谄。以取足恭之讥也。
文学在己。一有骄心。则其病真难医矣。必须在我者恒若不足。在人者切勿求备。汎爱容众。无取怨怒于人。而至于閒漫际接之间。亦当审其拜跪。谨其迎送。疾其报谢。要使适其亲疏贵贱尊卑贤愚之等而已。但不可葸而谄。以取足恭之讥也。容止必饬。
容止者。德之符也。若居而无可范之容。动而无可象之仪。则内何以取法于妻孥。外何以见重于朋侪哉。是故君子必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制其外以养其内。谨其容以收其心。固不可以修饰之末节而忽之也。盖其外之修整者。其中固未必尽皆谨严。而未有外不修整而心存者。然则君子之为学。其收敛安得不先从外面始也。且以相法言之。肩背竦直。步履安重者。吉人之相也。身体倾欹。衣襟摆乱者。贱人之相也。不惟智愚贤不肖于此判焉。寿夭穷达。亦可以卜矣。
言语必讱。
言语者。荣辱之机。祸福之门也。善哉金人之铭曰。无多言。多言多败。抑之篇曰。莫扪朕舌。言不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7H 页
 可逝矣。盖一出于口而不可复追者言也。可不讱乎。又况所与言者。或非精简慎密之人。则必致翻动唇舌。讹传赝添。甚至招灾速讼。陷身危辱。若择而后发。量而后出。则自无此患矣。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君子称之。而大传又曰吉人之辞寡。其他如讷言顾行尚口兴戎之戒垂于简册者。丁宁反覆。深切恳笃。宜服膺而顾諟也。
可逝矣。盖一出于口而不可复追者言也。可不讱乎。又况所与言者。或非精简慎密之人。则必致翻动唇舌。讹传赝添。甚至招灾速讼。陷身危辱。若择而后发。量而后出。则自无此患矣。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君子称之。而大传又曰吉人之辞寡。其他如讷言顾行尚口兴戎之戒垂于简册者。丁宁反覆。深切恳笃。宜服膺而顾諟也。闺门必肃。
闺门者。齐家之始也。未有闺门不肃而家齐者也。故家人之初以闲为吉。而终之以威如。必须谨内外之分。严男女之别。定户闼之限。简出入之节。正交接之际。以至巫觋僧尼牙婆市媪。亦一切远之。勿使频频往来。塞奇邪之途。绝非僻之干。则自然秩秩閒静而家道正矣。大抵闺门之内。恩常掩义。宽恕多而捡束难。又且妇人之性。不识义理。每以狎昵者为亲而谄媚者为爱。苟或顷刻而不知检。则怪举妄作。必有丈夫之所不及知。而甚或禽犊之行。出于门庭之内。丑不可闻。而家随而覆。可不惧哉。公父文伯之母。于季康子为从祖叔母之亲。而必䦱门而语之。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7L 页
 朱子已编之于小学。而至论古人治家之善。必曰雍穆。不但曰雍而又曰穆。则穆者敬也。其意可见也。
朱子已编之于小学。而至论古人治家之善。必曰雍穆。不但曰雍而又曰穆。则穆者敬也。其意可见也。交游必择。
交游者。人之所资以损益也。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处。如入鲍鱼之肆。蓬在麻中。不扶而直。沙在泥边。不染而黑。可不信所择欤。然不可者距之则失之隘。当汎爱而容之。有势者要之则伤于谄。当加敬而远之。但择其有学识操行好古守礼敦厚恬静者而亲之。则有患必得相恤而吾之急纾矣。有疑必得相质而吾之业广矣。有过必得相规而吾之德进矣。
租税必谨。
租税者。为民之职也。地必有税。税必有数。又必有时。今食其地之力。而欲减其数缓其时者。非道理也。世有力足以办。而强占气势。顽拒后时。自以为豪举者。甚不可也。敬谨奉公。趁期输纳。为编氓先。岂非士大夫之美事乎。又或悍官酷吏。不顾体面。差校临门。枷械加身。则实羞辱之大者也。若夫非理之征。无名之税。亦非在下者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8H 页
 所擅便则从众可也。
所擅便则从众可也。货财勿殖。
货财者。人之所赖以资活也。顾不重欤。然殖之则此取怨取祸之道也。大抵愚民但知用债之利。不知报债之艰。而又且欲随利长利。令智易昏。若或当报而不报。则吝于己之见失。而督责易至过度。能报而不报。则愤于彼之顽拒。而操束易至犯法。惹辱速讼。自是次第事耳。而为利戕身。不几于失轻重之伦乎。况执牙筹计债帐。没头役心。营营谋生。此市井牙侩之事。决非士大夫之所为也。苟贫不能资。或有待此而免死之时。只仅可取足而止。切不可贪利而务殖。以求饶而望富也。
方技勿狎。
方技者。固达理君子之所不屑好也。然学而至于达理尽不易。而吉凶祸福。亦人之所易动也。一或倾耳则不期于狎而自狎矣。然吉凶祸福。当求之于人事。而不当求之于恍惚杳冥之间也。且方技之流。类非端人。张浮驾诞。谝财取货。夸奇逞怪。惑世诬民者。十居八九。不肖子孙。无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8L 页
 识后生。往来亲熟。十斫之木。不能自树。因以妄谈休咎。传说图谶。则必有妄行祈禳之事。冀免倘来之厄。迁拔已安之厝。希求无妄之福。小则破家荡产。大则灾生虑表。连累罪过。丧身覆家。易如燎毛。岂不大可怕哉。明翁之绝河达海。此后学之所当取法也。
识后生。往来亲熟。十斫之木。不能自树。因以妄谈休咎。传说图谶。则必有妄行祈禳之事。冀免倘来之厄。迁拔已安之厝。希求无妄之福。小则破家荡产。大则灾生虑表。连累罪过。丧身覆家。易如燎毛。岂不大可怕哉。明翁之绝河达海。此后学之所当取法也。横逆勿较。
横逆者。无所致而至者也。无所致而至。则其较之也。或无怪矣。然不学之过也。我无所致则彼之横逆。乃彼之自为也。于我何干。于我何损哉。况此等人。元非良善可语之人。我无所致而犹横逆者。我若相较。则其横逆。不其愈甚矣乎。较而愈甚。终至于不可较之境。则初不如不较之为愈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忠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是亦禽兽而已矣。于禽兽又何难焉。若存得此心。则天下无可较之横逆矣。
是非勿参。
是非者。人之所不可无也。然有己之是非焉。有人之是非焉。己之是非不可无。人之是非不可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9H 页
 参也。设令吾之知识正当。闻见端的。判得直截。分明能是其真是。非其真非。见是者喜而见非者怒矣。万一吾之所是非者。不能得其真。则将如之何哉。况世末矣。无真是非久矣。何必以超然事外之身。自入于争竞之端。公然费吾之气力而惹人之唇舌也。然亦不可儱侗。都无分别。但采我薇蕨而守我太玄可也。
参也。设令吾之知识正当。闻见端的。判得直截。分明能是其真是。非其真非。见是者喜而见非者怒矣。万一吾之所是非者。不能得其真。则将如之何哉。况世末矣。无真是非久矣。何必以超然事外之身。自入于争竞之端。公然费吾之气力而惹人之唇舌也。然亦不可儱侗。都无分别。但采我薇蕨而守我太玄可也。分限勿过。
分限者。物之所不能齐也。有天定之分焉。有人事之分焉。寿夭穷达荣枯死生。天定之分也。尊卑贵贱贤愚强弱。人事之分也。天定之分。虽欲过之。非力所能容。固不须言。至于人事之分。亦有不可毫发差者。卑而抗尊则为不恭。贱而援贵则为不祥。愚而自处以贤则为妄。弱而自处以强则为悍。假如吃粥之人而吃饭则为不继矣。又假如吃饭之中。一匙之量而再匙三匙则胀矣。此目前易见之事也。然世之人不知此。而至于天定之分。亦欲力求过之。岂不悖哉。设或侥倖得遂。过一分则损一分。即天地盈虚消息自然之理也。己虽幸而得免。吾之后必有受其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79L 页
 报者。此亦不可不念也。古人曰知足。又曰量能。又曰遗有馀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存得此心。则身无败事而后必昌矣。
报者。此亦不可不念也。古人曰知足。又曰量能。又曰遗有馀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存得此心。则身无败事而后必昌矣。才艺勿矜。
才艺者末也。德行不能以副之。则君子反以为耻。况可矜之乎。矜之则硁硁乎。其为人可知矣。苟非龌龊偏窄之辈。即是浮薄轻佻之类耳。其所以矜之者。不过是夸衒扬耀。要以压倒人尔。然人之才亦非可以限数也。一有矜之之心。则必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强其所不能以为能者。万一锥颖未出而驴技已穷。一遇已知已能者与之对头。则窘跲露丑。将有不可胜言者。其为愧恧。不其甚于市朝之挞乎。又或世之信其虚声者。委之以过分难堪之事。则其偾误狼狈。可立而俟。而祸败随之。盆成括,骆宾王之事。可以监矣。
名誉勿求。
名誉者外也。有其实则自至。不可以求之也。一有求之之心。则必有巧言令色以求善之誉。擎拳曲跪以求恭之誉。讦摘工诃以求直之誉。惨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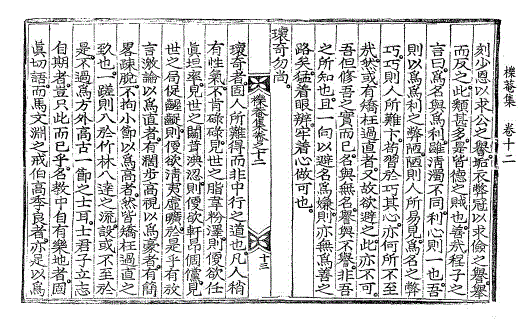 刻少恩以求公之誉。垢衣弊冠以求俭之誉。举而反之。此类甚多。是皆德之贼也。善哉程子之言曰。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利心则一也。吾则以为为利之弊陋。陋则人所易见。为名之弊巧。巧则人所难卞。苟习于巧其心。亦何所不至哉。然或有矫枉过直者。又故欲避之。此亦不可。吾但修吾之实而已。名与无名。誉与不誉。非吾之所知也。且一向以避名为嫌。则亦无为善之路矣。猛着眼辨。牢着心做可也。
刻少恩以求公之誉。垢衣弊冠以求俭之誉。举而反之。此类甚多。是皆德之贼也。善哉程子之言曰。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利心则一也。吾则以为为利之弊陋。陋则人所易见。为名之弊巧。巧则人所难卞。苟习于巧其心。亦何所不至哉。然或有矫枉过直者。又故欲避之。此亦不可。吾但修吾之实而已。名与无名。誉与不誉。非吾之所知也。且一向以避名为嫌。则亦无为善之路矣。猛着眼辨。牢着心做可也。瑰奇勿尚。
瑰奇者。固人所难得而非中行之道也。凡人稍有性气。不肯碌碌。见世之脂韦粉泽。则便欲任真坦率。见世之阘茸淟涊。则便欲轩昂倜傥。见世之局促龌龊。则便欲清夷虚旷。于是乎有放言激论以为直者。有阔步高视以为豪者。有简略疏脱。不拘小节以为高者。然皆矫枉过直之致也。一蹉则入于竹林八达之流。设或不至于是。不过为方外高古一节之士耳。士君子立志自期者。岂只此而已乎。名教中自有乐地者。固真切语。而马文渊之戒伯高季良者。亦足以为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0L 页
 法也。朱子释中庸之义曰庸平常也。人之日用当行平常之外。岂有他道也。
法也。朱子释中庸之义曰庸平常也。人之日用当行平常之外。岂有他道也。流俗勿徇。
流俗者。众所徇袭之称也。人既以瑰奇为不足尚。则其弊必至于同流合污浮沉取容。此则反不如瑰奇者之犹为脱俗超世之人也。大抵衰叔流俗之事。其合于义理者常小。而不合于义理者常多。不可以众所循袭而尽与之同也。生斯世也。善斯可也。非之无举。刺之无刺。此乡愿所以为德之贼也。程子曰。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者。不可从也。若其害于义者。虽以违世自异。至于取笑见怪。决不可恤也。
贵势勿耽。
贵势者。不可耽也。古人比之于炙手。又比之于冰山。手炙而未有身不病者。日出而未有冰未解者也。一有耽心。则身名轻而志节挫。廉耻丧而义理坏。笑骂从他。趍附恐后。蝇营狗苟。攘臂于指使之间。吮痈舐痔。混身于仆隶之列。小则灭身。大则流臭。如柳子厚之于王叔文。沈继祖之于韩侂胄。陷于收司连坐之律。归于鹰犬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1H 页
 矢之科而不知自拔。盖其初所以耽之者。不过丐其喉下之气以赌目前市童之怜。而为一世清议之唾鄙。为万古名教之罪人。岂不哀哉。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纵不能藐之。其又可耽之乎。切须戒之。
矢之科而不知自拔。盖其初所以耽之者。不过丐其喉下之气以赌目前市童之怜。而为一世清议之唾鄙。为万古名教之罪人。岂不哀哉。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纵不能藐之。其又可耽之乎。切须戒之。贫困勿厌。
贫困者。士之常也。不可厌也。命之定也。又非可以厌而免。苟有厌而欲免之心。则强者必至于非理行恶。弱者必至于摇尾乞丏。于是乎商贩牙侩之事。不耻为之。欺谝攘窃之术。不惮行之。嗟来之食。呼蹴之与。亦且甘而受之矣。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士也。设使厌而得免。失其肩背而养其一指。已不啻失其轻重之伦矣。又况厌之未必可免。则无乃只丧吾恒心而徒为人贱恶乎。夫子饮水曲肱而乐在其中。颜子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曾子捉襟而歌商颂。声出金石。圣贤之事。固不敢几而望之。然至若蕫邵南之渔樵耕读而不戚戚咨咨。陶渊明之夫耕妇锄而常有好容颜。顾不可引而为法乎。此为士者之所当励操处也。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1L 页
 祸患勿沮。
祸患勿沮。祸患之来。有由己者。有自外者。由己者。当恐惧修省之不暇。不但沮而止也。自外者。昔贤亦有不得免者。不当沮也。亦不足沮也。一遇倘来之厄。便自张皇摧挫。失其常度。则风吹草动。亦生畏㤼。志节消削。意气萧飒。无复有特立不屈之操。而与不学之人。无以异矣。寇莱公崖州一贬。反奏祥瑞。胡澹庵湖海十年。有情黎涡。程叔子自涪州还。髭发胜昔。蔡西山父子血脚讲论不掇。其得失何如也。朱子曰。使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正使岭海之外能死人。桁杨之下能殒人。有非关门塞窦所能免。淮舟遇风。岂章子厚所为。而臧氏之子。又安能使孟子不遇哉。决不可以此而沮吾向善守正之志也。
怨恨勿报。
人之处世。好恶殊道。爱憎多歧。而既不能每人而相悦。则人固有怨恨于吾。而吾亦不能无怨恨于人矣。若不问理之是非事之曲直。而一以报复为心。则狠愎忍毒。决非君子之用心矣。又况可乘之机。可报之势。不但吾有之。而彼亦有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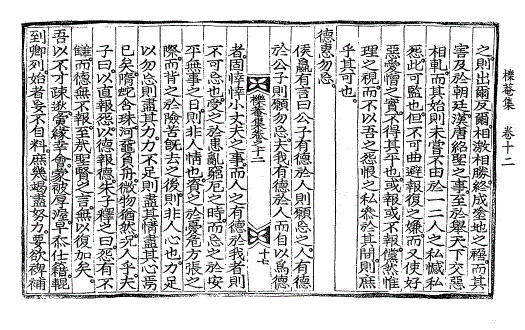 之。则出尔反尔。相激相胜。终成涂地之祸。而其害及于朝廷。汉唐绍圣之事。至于举天下交恶相轧。而其始则未尝不由于一二人之私憾私怨。此可监也。但不可曲避报复之嫌。而又使好恶爱憎之实。不得其平也。或报或不报。傥然惟理之视。而不以吾之怨恨之私参于其间。则庶乎其可也。
之。则出尔反尔。相激相胜。终成涂地之祸。而其害及于朝廷。汉唐绍圣之事。至于举天下交恶相轧。而其始则未尝不由于一二人之私憾私怨。此可监也。但不可曲避报复之嫌。而又使好恶爱憎之实。不得其平也。或报或不报。傥然惟理之视。而不以吾之怨恨之私参于其间。则庶乎其可也。德惠勿忘。
侯嬴有言曰公子有德于人则愿忘之。人有德于公子则愿勿忘。夫我有德于人而自以为德者。固悻悻小丈夫之事。而人之有德于我者则不可忘也。受之于患乱穷厄之时。而忘之于安平无事之日。则非人情也。资之于忧危方张之际。而背之于险苦既去之后。则非人心也。力足以勿忘则尽其力。力不足则尽其情尽其心焉已矣。隋蛇含珠。河鼋负舟。微物犹然。况人乎。夫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子释之曰。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至哉圣贤之言。无以复加矣。
吾以不才疏逖。夤缘幸会。蒙被厚渥。早忝仕籍。辊到卿列。始者妄不自料。庶几竭尽努力。要欲裨补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2L 页
 世教。不至为死而无闻之人。今老矣。朝暮将就木。而又累然作羁囚于千里穷海绝岛之中。顾念初心。直如画饼龙肉。不觉颜发骍而心忸怩。已矣不足复言矣。区区所望。惟在于吾所传之子孙。饬身谨行。不大有所忝于祖先成立之规。书此以遗。俾遵守焉。倘能体此苦心。念念顾諟。不使乃祖乃父为空言之鬼而含羞于地中。则幸之幸也。过此以往。又有心地上一端根本工夫。而余未及言之。此则在当者之各各加之意也。
世教。不至为死而无闻之人。今老矣。朝暮将就木。而又累然作羁囚于千里穷海绝岛之中。顾念初心。直如画饼龙肉。不觉颜发骍而心忸怩。已矣不足复言矣。区区所望。惟在于吾所传之子孙。饬身谨行。不大有所忝于祖先成立之规。书此以遗。俾遵守焉。倘能体此苦心。念念顾諟。不使乃祖乃父为空言之鬼而含羞于地中。则幸之幸也。过此以往。又有心地上一端根本工夫。而余未及言之。此则在当者之各各加之意也。前十四条。修己治家处世之道。亦略备矣。复益之以后十四条者。盖好仁而不知恶不仁。则不仁者或有时而加诸我矣。向善而不知远不善。则不善者或有时而及于身矣。亦孟子所谓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之意也。
此二十八条。过则贤。及则为清修之吉士。不及亦足为承家之肖孙也。
为吾子孙者。每于吾之死日及正至月朔。齐会于吾之庙前。年长者通读一遍。使诸子诸孙。敬恭谛听。服膺遵守。而如有不率教者。又相与挞之于吾之庙前。以是责罚。如是而又不率教。则生不可以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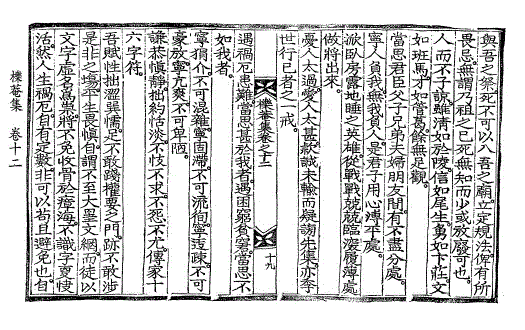 与吾之祭。死不可以入吾之庙。立定规法。俾有所畏忌。无谓乃祖之已死无知而少或放废可也。
与吾之祭。死不可以入吾之庙。立定规法。俾有所畏忌。无谓乃祖之已死无知而少或放废可也。人而不子谅。虽清如于陵。信如尾生。勇如卞庄。文如班马。才如管葛。馀无足观。
当思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有不尽分处。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是君子用心溥平处。
掀卧房露地睡之英雄。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
忧人太过。爱人太甚。款诚未输而疑谤先集。亦季世行己者之一戒。
遇祸厄患难。当思甚于我者。遇困穷贫窘。当思不如我者。
宁狷介。不可混杂。宁固滞。不可流徇。宁迂疏。不可豪放。宁亢爽。不可卑陋。
谦恭慎静。拙约恬淡。不忮不求。不怨不尤。传家十六字符。
吾赋性拙涩巽懦。足不敢践权要之门。迹不敢涉是非之场。平生畏慎。自谓不至大挂文网。而徒以文字虚名为祟。将不免收骨于瘴海。不识字更快活。然人生祸厄。自有定数。非可以苟且避免也。自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3L 页
 古不读书而遭祸厄者何限。今以此归咎于书则误矣。况书中所说道理。无非做人样子。不读书而能为人者。吾未之闻矣。慎勿以吾为戒。而勉旃勉旃。
古不读书而遭祸厄者何限。今以此归咎于书则误矣。况书中所说道理。无非做人样子。不读书而能为人者。吾未之闻矣。慎勿以吾为戒。而勉旃勉旃。良已(金溪录)
昭明累人。居谪之数月。病痰痞。膈阏而喉涩。行则聩聩。居则圉圉。心患之。就诸医。求所以已之。医曰。不可以药也。已之在心。夫痞气之积而不泄者也。气顺则自去。顺气之道无他。心而已。夫心气之帅也。气心之卒徒也。子独不见夫水与木乎。水失其性而后。横溃汎滥。木瘁其根而后。蠹生之。今恶其横与蠹。而沙石以遏之。斧斤以削之。其横愈甚。而其蠹终不可去矣。亦在乎疏之而已。固之而已。譬之兵。将失其驭。则军不得其平而叫欢强凌。犯上之难起。非威刑斩伐之可制也。故善将者。亦视其驭之何如耳。噫。子之将失其驭。而其根瘁矣。其横溃汎滥。叫欢强凌。固无怪也。于是而不反其本。姑斩伐以威之。斧斤以削之。吾恐子之病将为癨为疝为癖。而但痞乎而望其已乎。亦在乎顺之而已。余闻之始疑之。既已曰可思也。其古人斲轮之遗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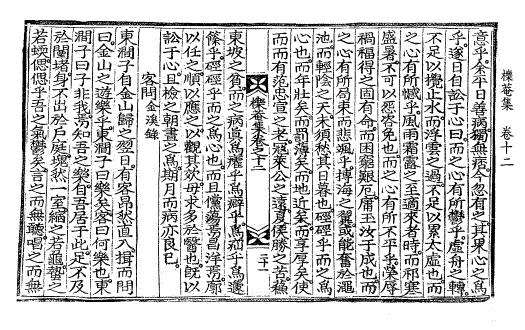 意乎。余平日善病。独无痞。今忽有之。其果心之为乎。遂日自讼于心曰。而之心有所郁乎。虚舟之转。不足以搅止水。而浮云之过。不足以累太虚也。而之心有所憾乎。风雨霜露之至适来者时。而祁寒盛暑。不可以怨咨免也。而之心有所不平乎。荣辱祸福得之固有命。而困穷艰厄。庸玉汝于成也。而之心有所局束而悲飒乎。抟海之翼。或能奋于渑池。而轻阴之天。未须愁其日暮也。硁硁乎而之为心也。而年壮矣。而罚薄矣。而地近矣。而享厚矣。使而而有范忠宣之老。寇莱公之远。夏侯胜之苦。苏东坡之贫。而之病真为癨乎为癖乎。为疝乎为籧篨乎。硁硁乎而之为心也。而且傥荡焉昌洋焉。廓以任之。顺以应之。以观其效。毋求多于医也。既以讼于心。且检之朝昼之为。期月而病亦良已。
意乎。余平日善病。独无痞。今忽有之。其果心之为乎。遂日自讼于心曰。而之心有所郁乎。虚舟之转。不足以搅止水。而浮云之过。不足以累太虚也。而之心有所憾乎。风雨霜露之至适来者时。而祁寒盛暑。不可以怨咨免也。而之心有所不平乎。荣辱祸福得之固有命。而困穷艰厄。庸玉汝于成也。而之心有所局束而悲飒乎。抟海之翼。或能奋于渑池。而轻阴之天。未须愁其日暮也。硁硁乎而之为心也。而年壮矣。而罚薄矣。而地近矣。而享厚矣。使而而有范忠宣之老。寇莱公之远。夏侯胜之苦。苏东坡之贫。而之病真为癨乎为癖乎。为疝乎为籧篨乎。硁硁乎而之为心也。而且傥荡焉昌洋焉。廓以任之。顺以应之。以观其效。毋求多于医也。既以讼于心。且检之朝昼之为。期月而病亦良已。客问(金溪录)
东涧子自金山归之翌日。有客昂然直入。揖而问曰。金山之游乐乎。东涧子曰乐矣。客曰何乐也。东涧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之乐。自吾居于此。足不及于闉堵。身不出于户庭。块然一室。缩之若龟。蛰之若蠕。偲偲乎吾之气郁矣。言之而无听。唱之而无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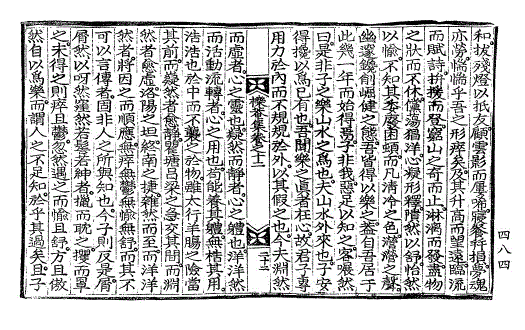 和。拔残灯以抵友。顾云影而屡唏。寝餐并损。梦魂亦劳。惴惴乎吾之形瘁矣。及其升高而望远。临流而赋诗。拚援而登。穷山之奇而止。淋漓而发。尽物之状而不休。傥荡猖洋。心凝形释。隤然以舒。怡然以愉。不知其委废困顿。而凡清冷之色。瀯瀯之声。幽邃镵削崛健之态。吾皆得以乐之。盖自吾居于此几一年而始得焉。子非我。恶足以知之。客𠹖然曰。是非子之乐山水之为也。夫山水外来也。子安得搀以为己有也。吾闻乐之真者在心。故君子专用力于内而不规规于外。以其假之也。今夫渊然而虚者。心之灵也。嶷然而静者。心之体也。洋洋然而活动流转者。心之用也。苟能养其体。无梏其用。浩浩也于中而不袭之于物。虽太行羊肠之险当其前。而嶷然者愈静。瞿塘吕梁之急交其间。而渊然者愈虚。洛阳之坦。终南之捷。杂然而至。而洋洋然者。将因之而顺应。无瘁无郁无愉无舒。而其不可以言传者。固非人之所与知也。今子则反是。屑屑然以呀然洼然若髻若绅者。擸而耽之。攫而罩之。未得之则瘁且郁。忽然遇之而愉且舒。方且傲然自以为乐。而谓人之不足知。于乎其过矣。且子
和。拔残灯以抵友。顾云影而屡唏。寝餐并损。梦魂亦劳。惴惴乎吾之形瘁矣。及其升高而望远。临流而赋诗。拚援而登。穷山之奇而止。淋漓而发。尽物之状而不休。傥荡猖洋。心凝形释。隤然以舒。怡然以愉。不知其委废困顿。而凡清冷之色。瀯瀯之声。幽邃镵削崛健之态。吾皆得以乐之。盖自吾居于此几一年而始得焉。子非我。恶足以知之。客𠹖然曰。是非子之乐山水之为也。夫山水外来也。子安得搀以为己有也。吾闻乐之真者在心。故君子专用力于内而不规规于外。以其假之也。今夫渊然而虚者。心之灵也。嶷然而静者。心之体也。洋洋然而活动流转者。心之用也。苟能养其体。无梏其用。浩浩也于中而不袭之于物。虽太行羊肠之险当其前。而嶷然者愈静。瞿塘吕梁之急交其间。而渊然者愈虚。洛阳之坦。终南之捷。杂然而至。而洋洋然者。将因之而顺应。无瘁无郁无愉无舒。而其不可以言传者。固非人之所与知也。今子则反是。屑屑然以呀然洼然若髻若绅者。擸而耽之。攫而罩之。未得之则瘁且郁。忽然遇之而愉且舒。方且傲然自以为乐。而谓人之不足知。于乎其过矣。且子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5H 页
 能外形骸。群鸟兽餐霞瀣。恒得与是山水为伍乎。否者人之所谓乐者迁矣。曾是以迁者而谓之乐乎。若此者吾不愿知之。言未卒。东涧子矍然敛容而谢曰。先生休矣。吾知之矣。行且勉焉。须臾客去。遂书其语以为戒。
能外形骸。群鸟兽餐霞瀣。恒得与是山水为伍乎。否者人之所谓乐者迁矣。曾是以迁者而谓之乐乎。若此者吾不愿知之。言未卒。东涧子矍然敛容而谢曰。先生休矣。吾知之矣。行且勉焉。须臾客去。遂书其语以为戒。书伯氏书赠格言后
右我伯氏所书赠者。计始赠时。余年才成童。而勉之若是其勤。期之若是其深。虽父兄之望子弟。其情或无怪焉。自度若全无省识。亦无以得此者。今去彼时几二十年。将童而翁矣。宜其期勉之者。有加于前。而伯氏亦不复以此等语见赠。是则盖不屑之意也。然其中间自弃。从可知矣。于乎其负之矣。继自今欲易心改图。自期自勉。以少收桑榆。亦庶几不至终负。而且以望复有所期勉于伯氏云尔。岁己酉立春后三日。季弟晋奎谨书。
书沙矶李忠贞公(是远)殉节后
沙矶李公之死。余哭之出涕。其葬也。又为诗二百十言以哀之。甚恨平日不能一识其颜貌。既而闻世之疵謷公者龂龂也。其言曰不识寇之将至而先去之。是不智也。寇至而不能乘一障以与贼抗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5L 页
 而徒死之。是无勇也。社稷宗庙无恙而先死之。是不仁也。无封疆之守军旅之责而轻死之。是无义也。无识者倡之而有识者和焉。余闻而伤之曰。甚矣其为言也。夫死者人之所甚难也。不难其甚难。而独讥诋之不已。彼难之者又将何说。然今不闻斥其难之者。而独斥其不难者。吁诚不可知也。君子之致身于国也。惟其所在则尽节。不以进退缓急而计较之也。使为人臣而遭祸难者。苟皆曰我无守也。我无责也。轻死非义也。否则曰国未亡先死非仁也。贼未抗徒死非勇也。甚者知机而避。先事而逃。而犹自以为智。则自古忠臣烈士之当死者无几人。而得免于不仁不义之科者亦鲜矣。昔江万里以故相死于饶州。是时宋之社稷宗庙尚无恙。而亦非有封疆军旅之责也。壬辰之乱。梁山郡守文某越境而赴东莱死之。非其守也而人诵慕之无二辞。未有以先死轻死咎二公也。此犹衣食君者耳。彼尹谷欧阳澈之死。果有责有守焉者乎。亦未有以轻死咎之也。而独苛于公。如彼无顾忌。岂忠义之感于人。或有古今之异。而大伦之在天地间者。亦有时而轩轾乎。何其议论之不相及
而徒死之。是无勇也。社稷宗庙无恙而先死之。是不仁也。无封疆之守军旅之责而轻死之。是无义也。无识者倡之而有识者和焉。余闻而伤之曰。甚矣其为言也。夫死者人之所甚难也。不难其甚难。而独讥诋之不已。彼难之者又将何说。然今不闻斥其难之者。而独斥其不难者。吁诚不可知也。君子之致身于国也。惟其所在则尽节。不以进退缓急而计较之也。使为人臣而遭祸难者。苟皆曰我无守也。我无责也。轻死非义也。否则曰国未亡先死非仁也。贼未抗徒死非勇也。甚者知机而避。先事而逃。而犹自以为智。则自古忠臣烈士之当死者无几人。而得免于不仁不义之科者亦鲜矣。昔江万里以故相死于饶州。是时宋之社稷宗庙尚无恙。而亦非有封疆军旅之责也。壬辰之乱。梁山郡守文某越境而赴东莱死之。非其守也而人诵慕之无二辞。未有以先死轻死咎二公也。此犹衣食君者耳。彼尹谷欧阳澈之死。果有责有守焉者乎。亦未有以轻死咎之也。而独苛于公。如彼无顾忌。岂忠义之感于人。或有古今之异。而大伦之在天地间者。亦有时而轩轾乎。何其议论之不相及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6H 页
 而相戾耶。至以不能先去而不能抗贼为公咎者。尤不满一笑。夫死者只是成就一个义而已。处可抗之任则抗而不胜而死义也。无其任则不得抗而死亦义也。抗与不抗。固非死与不死之准。而惟去则为苟免。故君子之见危授命。以不去为义。苟或有邂逅避免者。则或先或后虽不同。同归于不义。故不知而去犹可也。知则不可去矣。然则使公而虽知之。必不以己无其任而为不义之去也。况彼之闪倏出没无常。滨海数千里。皆其所窥觇。又安知其必出于江都也。今乃以不足为准者。拟之于不当其任之地。而又以其不可必知与知而不为者。欲为公而苟免。不然则遂直以不仁不义断之。是果知仁义之为美而伤其过者乎。抑不便于贪生自私之计而姑托是以工诃者乎。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曰。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圣贤之言仁义。不过如此。而今之人。一切反是而为言。其亦异乎吾所闻矣。于乎当时之事惨矣。留守逃中军窜。经历避之。其他拥强兵。环而视者。夫孰非有责有守者。而不敢出一头向前枝梧。一朝而举金汤天堑之重。拱手与
而相戾耶。至以不能先去而不能抗贼为公咎者。尤不满一笑。夫死者只是成就一个义而已。处可抗之任则抗而不胜而死义也。无其任则不得抗而死亦义也。抗与不抗。固非死与不死之准。而惟去则为苟免。故君子之见危授命。以不去为义。苟或有邂逅避免者。则或先或后虽不同。同归于不义。故不知而去犹可也。知则不可去矣。然则使公而虽知之。必不以己无其任而为不义之去也。况彼之闪倏出没无常。滨海数千里。皆其所窥觇。又安知其必出于江都也。今乃以不足为准者。拟之于不当其任之地。而又以其不可必知与知而不为者。欲为公而苟免。不然则遂直以不仁不义断之。是果知仁义之为美而伤其过者乎。抑不便于贪生自私之计而姑托是以工诃者乎。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曰。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圣贤之言仁义。不过如此。而今之人。一切反是而为言。其亦异乎吾所闻矣。于乎当时之事惨矣。留守逃中军窜。经历避之。其他拥强兵。环而视者。夫孰非有责有守者。而不敢出一头向前枝梧。一朝而举金汤天堑之重。拱手与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6L 页
 之。而独使公当其不幸。向非公于仁义之道。知之明而决之勇。以渺然七尺之躯。自任以纲常之重。吾恐其歘然决裂之所及。不但一江都而止耳。环东土礼义之邦。其有不胥沦于夷狄禽兽之域者乎。卒乃逡巡敛其冲突而不敢肆者。果谁惮而然也。若公者真可谓仁者之勇。而其功非一时摧陷之所可比也。此不待智者而后知。而反从而尤之。又设淫辞以助之攻。甚矣其心之不仁而其言之敢于不义也。率天下而陷于遗君后国者。必此为之祸也。方乱时。余适在京师。有自江都来者言公所居距城稍远。及闻变入赴则城已陷。事无可为矣。公犹策一驴。周城三日。求见一官人而不能得。公死时阳阳如他日。绝无怨悔之意。尝和药一仰而不遂。至再仰乃绝。其后得公遗疏。又得公绝命诗。最后又得公之弟监役所为日记者。大率见于辞气者。温厚恻怛。不为矫矜激发。而自有凛然不可犯者。其所论国家事。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余有先墓在金陵。于江都邻也。尝往来金陵间。金陵人为余言公初为畿辅直指。风裁自持。虽强不吐。坐是坎壈数十年。后按北闑。不挫益励。而惟孜孜
之。而独使公当其不幸。向非公于仁义之道。知之明而决之勇。以渺然七尺之躯。自任以纲常之重。吾恐其歘然决裂之所及。不但一江都而止耳。环东土礼义之邦。其有不胥沦于夷狄禽兽之域者乎。卒乃逡巡敛其冲突而不敢肆者。果谁惮而然也。若公者真可谓仁者之勇。而其功非一时摧陷之所可比也。此不待智者而后知。而反从而尤之。又设淫辞以助之攻。甚矣其心之不仁而其言之敢于不义也。率天下而陷于遗君后国者。必此为之祸也。方乱时。余适在京师。有自江都来者言公所居距城稍远。及闻变入赴则城已陷。事无可为矣。公犹策一驴。周城三日。求见一官人而不能得。公死时阳阳如他日。绝无怨悔之意。尝和药一仰而不遂。至再仰乃绝。其后得公遗疏。又得公绝命诗。最后又得公之弟监役所为日记者。大率见于辞气者。温厚恻怛。不为矫矜激发。而自有凛然不可犯者。其所论国家事。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余有先墓在金陵。于江都邻也。尝往来金陵间。金陵人为余言公初为畿辅直指。风裁自持。虽强不吐。坐是坎壈数十年。后按北闑。不挫益励。而惟孜孜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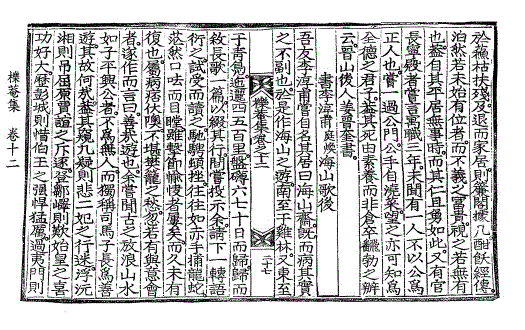 于苏枯扶残。及退而家居。则帘阁据几。酣饫经传。泊然若未始有位者。而不义之富贵。视之若无有也。盖自其平居无事时。而其仁且勇如此。又有官长宁殿者尝言寓职三年。未闻有一人不以公为正人也。尝一过公门。公手自浇菜。望之亦可知为全德之君子。盖其死由素养而非仓卒翻勃之办云。晋山后人姜晋奎书。
于苏枯扶残。及退而家居。则帘阁据几。酣饫经传。泊然若未始有位者。而不义之富贵。视之若无有也。盖自其平居无事时。而其仁且勇如此。又有官长宁殿者尝言寓职三年。未闻有一人不以公为正人也。尝一过公门。公手自浇菜。望之亦可知为全德之君子。盖其死由素养而非仓卒翻勃之办云。晋山后人姜晋奎书。书李淳甫(庭焕)海山歌后
吾友李淳甫尝自名其居曰海山斋。既而病其实之不副也。于是作海山之游。南至于鸡林。又东至于青凫。迤逦四五百里。盘礴六七十日而归。归而叙长歌一篇。以缀其行。间尝投示余。请下一转语衍之。试受而读之。驰骋顿挫。往往如赤手捕龙蛇。茫然口呿而目瞠。虽击节愉快者屡矣。而久未有复也。属病痞伏隩。不堪樊笼之愁。忽若有与意会者。遂作而言曰。善哉游也。余尝闻古之放浪山水如子平兴公者。不为无人。而独称司马子长为善游。其故何哉。盖其窥九疑则悲二妃之行迷。浮沅湘则吊屈原贾谊之斥逐。登邹峄则叹始皇之喜功好大。历彭城则惜伯王之强悍猛厉。过夷门则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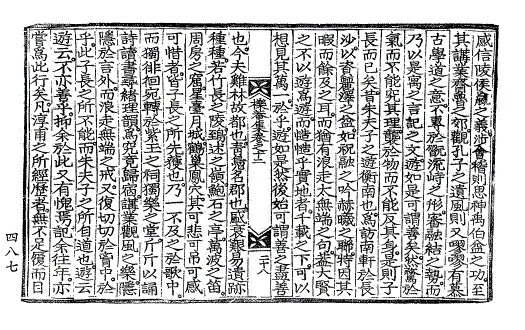 感信陵侯嬴之义。涉会稽则思神禹伯益之功。至其讲业齐鲁之郊。观孔子之遗风则又嘐嘐有慕古学道之意。不专于玩流峙之形。审融结之势。而乃以是寓之言记之文。游如是可谓善矣。然骛于气而不能究其理。袭于物而不能反其身。是则子长而已矣。昔朱夫子之游衡南也。为访南轩于长沙。以资丽泽之益。如祝融之吟赫曦之联。特因其暇而馀及之耳。而犹有浪走太无端之句。盖大贤之不以游为游。而慥慥乎实地者。千载之下。可以想见其万一。于乎。游如是然后始可谓善之尽善也。今夫鸡林故都也。青凫名郡也。盛衰艰易遗迹种种。若竹长之陵。鸱述之岭。鲍石之亭。万波之笛。周房之窟。星台月城。鹤巢凤穴。其可悲可吊可感可惜者。皆子长之所先获也。乃一不及之于歌中。而独徘徊宛转于紫玉之祠独乐之堂。斤斤以诵诗读书寻绪理韵。为究竟归宿。讲业观风之乐。隐隐于言外。而浪走无端之戒。又复切切于胸中。于乎。此子长之所不能。而朱夫子之所自道也。游云游云。不亦善乎。抑余于此又有愧焉。记余往年。亦尝为此行矣。凡淳甫之所经历者。无不足履而目
感信陵侯嬴之义。涉会稽则思神禹伯益之功。至其讲业齐鲁之郊。观孔子之遗风则又嘐嘐有慕古学道之意。不专于玩流峙之形。审融结之势。而乃以是寓之言记之文。游如是可谓善矣。然骛于气而不能究其理。袭于物而不能反其身。是则子长而已矣。昔朱夫子之游衡南也。为访南轩于长沙。以资丽泽之益。如祝融之吟赫曦之联。特因其暇而馀及之耳。而犹有浪走太无端之句。盖大贤之不以游为游。而慥慥乎实地者。千载之下。可以想见其万一。于乎。游如是然后始可谓善之尽善也。今夫鸡林故都也。青凫名郡也。盛衰艰易遗迹种种。若竹长之陵。鸱述之岭。鲍石之亭。万波之笛。周房之窟。星台月城。鹤巢凤穴。其可悲可吊可感可惜者。皆子长之所先获也。乃一不及之于歌中。而独徘徊宛转于紫玉之祠独乐之堂。斤斤以诵诗读书寻绪理韵。为究竟归宿。讲业观风之乐。隐隐于言外。而浪走无端之戒。又复切切于胸中。于乎。此子长之所不能。而朱夫子之所自道也。游云游云。不亦善乎。抑余于此又有愧焉。记余往年。亦尝为此行矣。凡淳甫之所经历者。无不足履而目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8H 页
 睹。顾当时风埃乾没。尘土满襟。只从一场逆旅。醉梦中过。非但业之无所于讲。风之无所于观。而以至流峙之形。融结之势。亦都无毫分领略留者。及今倦于四方。终日空堂。卧念旧游。杳然龙汉㥘外。而淳甫之歌。起余一番四十年宿生结习。忽不觉奕奕然矣。亟欲挟一奚。负筒而走。重致身于山光海色之间。以复雁门之踦。而衰甚矣。末由也已。宁抱我简结我线拭我弦。自附于后尘。共此家计于究竟归宿之地。庶使前日之逆旅醉梦。或不至于大脱空也。未知淳甫不以为僭而呵斥。容其一榻于坐侧否乎。
睹。顾当时风埃乾没。尘土满襟。只从一场逆旅。醉梦中过。非但业之无所于讲。风之无所于观。而以至流峙之形。融结之势。亦都无毫分领略留者。及今倦于四方。终日空堂。卧念旧游。杳然龙汉㥘外。而淳甫之歌。起余一番四十年宿生结习。忽不觉奕奕然矣。亟欲挟一奚。负筒而走。重致身于山光海色之间。以复雁门之踦。而衰甚矣。末由也已。宁抱我简结我线拭我弦。自附于后尘。共此家计于究竟归宿之地。庶使前日之逆旅醉梦。或不至于大脱空也。未知淳甫不以为僭而呵斥。容其一榻于坐侧否乎。谕欕木文
天地之间。明则有人。幽则有鬼神。幽不可以干明。鬼不可以逼人。盖自重黎氏分属以来。截然莫或相杂糅也。其有一种坱莽之气。郁而不散。轮囷轧轖。或闪而为燐。或砉而为啸。或种于物而为草木土石虫鱼鳞甲之类。久而不胜其亭毒悭蛰之势。时出而宣泄之。大率陆处者屏于陆。水居者屏于水。不过自相依附自相欱嘘。以自神其灵异而已。如天吴应龙。抃海之鳌。抟风之鹏。九转之砂。三叉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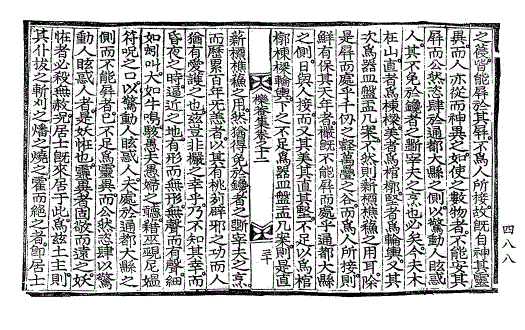 之蔘。皆能屏于其屏。不为人所接。故既自神其灵异。而人亦从而神异之。如使之数物者。不能安其屏而公然恣肆于通都大县之侧。以惊动人眩惑人。其不免于镵者之斲宰夫之烹也必矣。今夫木在山。直者为栋梁。美者为棺椁。坚者为轮舆。又其次为器皿盘盂几案。不然则薪槱樵苏之用耳。除是屏而处乎千仞之壑万叠之谷。而为人所接。则鲜有保其天年者。欕既不能屏而处乎通都大县之侧。日与人接。而又其美其直其坚。不足以为棺椁栋梁轮舆。下之不足为器皿盘盂几案。则是直薪槱樵苏之用。然犹得免于镵者之斲宰夫之烹。而历累百年无恙者。以其有桃茢辟邪之功而人犹有爱护之也。玆岂非欕之幸乎。乃不知其幸。而昏夜之时。逼近之地。有形而无形。无声而有声。细如蚓叫。大如牛鸣。骇愚夫愚妇之听。藉巫觋尼媪符咒之口。以惊动人眩惑人。夫处于通都大县之侧而不能屏者。已不足为灵异。而公然恣肆以惊动人眩惑人者。是妖怪也。灵异者固敬而远之。妖怪者必杀无赦。况居士既来居于此。为玆土主。则其仆拔之斩刈之燔之烧之霍而绝之者。即居士
之蔘。皆能屏于其屏。不为人所接。故既自神其灵异。而人亦从而神异之。如使之数物者。不能安其屏而公然恣肆于通都大县之侧。以惊动人眩惑人。其不免于镵者之斲宰夫之烹也必矣。今夫木在山。直者为栋梁。美者为棺椁。坚者为轮舆。又其次为器皿盘盂几案。不然则薪槱樵苏之用耳。除是屏而处乎千仞之壑万叠之谷。而为人所接。则鲜有保其天年者。欕既不能屏而处乎通都大县之侧。日与人接。而又其美其直其坚。不足以为棺椁栋梁轮舆。下之不足为器皿盘盂几案。则是直薪槱樵苏之用。然犹得免于镵者之斲宰夫之烹。而历累百年无恙者。以其有桃茢辟邪之功而人犹有爱护之也。玆岂非欕之幸乎。乃不知其幸。而昏夜之时。逼近之地。有形而无形。无声而有声。细如蚓叫。大如牛鸣。骇愚夫愚妇之听。藉巫觋尼媪符咒之口。以惊动人眩惑人。夫处于通都大县之侧而不能屏者。已不足为灵异。而公然恣肆以惊动人眩惑人者。是妖怪也。灵异者固敬而远之。妖怪者必杀无赦。况居士既来居于此。为玆土主。则其仆拔之斩刈之燔之烧之霍而绝之者。即居士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9H 页
 责也。然犹惜其以辟邪之功而反自陷于妖怪。又不忍其累百年之幸而一朝不幸。姑缓之而为文以与欕约。如果欕之所自为也。当戢其声閟其鸣。无自取仆拔斩刈燔烧之祸。设或他物之所凭而假欕为之。环岭峤绝壑深谷之中。千章之栎。百围之檀。蔽日之榆。干云之杉。可凭而可假者无数也。亦当其避而去之。毋自失其所凭也。若其暋不听念。悍然不如约。是自恃其妖怪。以与居士抗。居士虽驽甚。平生读圣贤书。粗能知鬼神之情状。又尝位于朝。光显掌杀活之权。即毋论欕与他物。决不任其恣为妖怪于逼近之地。而坐视其惊动眩惑人于通都大县之恻也。当手执殳先之。继以刽子前梓人后。健夫猛丁。蜂拥而至。长絙铁帚。一齐并举。不崇朝而皮肉狼藉。骨节粉碎。然后夷其窍堑其墟。投之以烈焰。灌之以沸釜。片柯只叶。无遗乃已。于是也虽欲戢而閟之。避而去之。以毋取其祸。毋失其凭得乎。昔南山之佛。顺程伯子之令。而身首不异处。潮州之鳄。听退之之言而免强弓劲弩之害。庙庭之蛇。不识孔道辅而终被杀死。即毋论欕与他物。欲自为灵异而不为妖怪。于斯三者何
责也。然犹惜其以辟邪之功而反自陷于妖怪。又不忍其累百年之幸而一朝不幸。姑缓之而为文以与欕约。如果欕之所自为也。当戢其声閟其鸣。无自取仆拔斩刈燔烧之祸。设或他物之所凭而假欕为之。环岭峤绝壑深谷之中。千章之栎。百围之檀。蔽日之榆。干云之杉。可凭而可假者无数也。亦当其避而去之。毋自失其所凭也。若其暋不听念。悍然不如约。是自恃其妖怪。以与居士抗。居士虽驽甚。平生读圣贤书。粗能知鬼神之情状。又尝位于朝。光显掌杀活之权。即毋论欕与他物。决不任其恣为妖怪于逼近之地。而坐视其惊动眩惑人于通都大县之恻也。当手执殳先之。继以刽子前梓人后。健夫猛丁。蜂拥而至。长絙铁帚。一齐并举。不崇朝而皮肉狼藉。骨节粉碎。然后夷其窍堑其墟。投之以烈焰。灌之以沸釜。片柯只叶。无遗乃已。于是也虽欲戢而閟之。避而去之。以毋取其祸。毋失其凭得乎。昔南山之佛。顺程伯子之令。而身首不异处。潮州之鳄。听退之之言而免强弓劲弩之害。庙庭之蛇。不识孔道辅而终被杀死。即毋论欕与他物。欲自为灵异而不为妖怪。于斯三者何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89L 页
 择焉。居士之为程为韩为孔。亦当视其所择而与之从事。其审图之毋悔。
择焉。居士之为程为韩为孔。亦当视其所择而与之从事。其审图之毋悔。读梓材(镜湖录)
余读梓材书。尝切反复而疑之曰。古者简册。历世既久。错者有之。脱者有之。合者亦有之。错而脱者。不过几字几句。其合者亦上下文理语脉之相连续者耳。曷尝有二篇合为一篇者乎。当时传书者。亦应博雅达古之士。岂有全不识上下文理语脉之不同。而徒以字之相似意之相近。强合而为一乎。伏生以来。自汉迄宋。博雅达古之士。又代不乏人。何徒无一人言之。而独至于蔡氏而言之也。且康叔周之名臣也。武王之称康叔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其期望倚毗。周召以外无及焉。其亦周召之亚也。进戒之辞。周公居多。召公次之。夫以周召之亚。而上之所以期望倚毗者。又如此其至。乃无一言仰答乎。是皆不可晓也。读之愈久而疑之愈深。既而涣然悟曰。此非烂简也。无胥戕以下。即康叔之辞。而蔡氏误以为他书之合也。请试明之。夫妹土之染恶。武王之所深忧也。故以诰毖丕变之责。择人而命康叔。其言曰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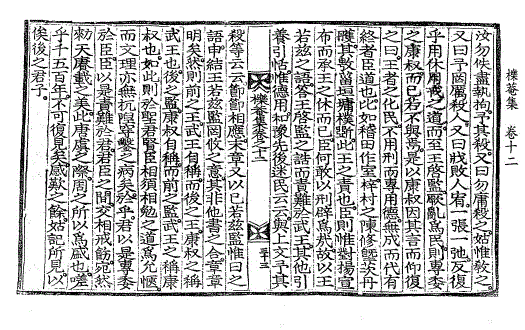 汝勿佚尽执拘。予其杀。又曰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又曰予罔厉杀人。又曰戕败人宥。一张一弛。反复乎用休用戎之道。而至王启监。厥乱为民。则专委之康叔。而己若不与焉。是以康叔因其言而仰复之曰。王者之化民。不用刑而专用德。无成而代有终者臣道也。比如稽田作室。梓村之陈修塈茨丹雘。其敷菑垣墉朴斲。此王之责也。臣则惟对扬宣布而承王之休而已。臣何敢以刑辟为哉。故以王若玆之语。答王启监之诰而责难于武王。其他引养引恬。惟德用。和豫先后迷民云云。与上文予其杀等云云。节节相应。末章又以己若玆监惟曰之语。申结王若玆监罔攸之意。其非他书之合。章章明矣。然则前之王。武王自称。而后之王。康叔之称武王也。后之监。康叔自称。而前之监。武王之称康叔也。如此则于圣君贤臣相须相勉之道为允惬。而文理亦无扤隉穿凿之病矣。于乎。君以是专委于臣。臣以是责难于君。君臣之间。交相戒饬。宛然敕天赓载之美。此唐虞之际。周之所以为盛也。嗟乎千五百年。不可复见矣。感叹之馀。姑记所见。以俟后之君子。
汝勿佚尽执拘。予其杀。又曰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又曰予罔厉杀人。又曰戕败人宥。一张一弛。反复乎用休用戎之道。而至王启监。厥乱为民。则专委之康叔。而己若不与焉。是以康叔因其言而仰复之曰。王者之化民。不用刑而专用德。无成而代有终者臣道也。比如稽田作室。梓村之陈修塈茨丹雘。其敷菑垣墉朴斲。此王之责也。臣则惟对扬宣布而承王之休而已。臣何敢以刑辟为哉。故以王若玆之语。答王启监之诰而责难于武王。其他引养引恬。惟德用。和豫先后迷民云云。与上文予其杀等云云。节节相应。末章又以己若玆监惟曰之语。申结王若玆监罔攸之意。其非他书之合。章章明矣。然则前之王。武王自称。而后之王。康叔之称武王也。后之监。康叔自称。而前之监。武王之称康叔也。如此则于圣君贤臣相须相勉之道为允惬。而文理亦无扤隉穿凿之病矣。于乎。君以是专委于臣。臣以是责难于君。君臣之间。交相戒饬。宛然敕天赓载之美。此唐虞之际。周之所以为盛也。嗟乎千五百年。不可复见矣。感叹之馀。姑记所见。以俟后之君子。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0L 页
 居閒琐录
居閒琐录汉昭烈不受荆州于刘表之让。又不取荆州于刘琮之降。程子亦以后一着为失计。然此昭烈杂霸之术。假买人情者。观后来取刘璋。则可知其言之非出于诚心也。刘璋岂非昭烈之同宗。而又岂非厚于昭烈者乎。盖荆州吴魏之所必争。而昭烈又魏之所最忌者也。昭烈以狼狈奔窜之馀。方为魏所逐。而一朝坐而得之。处其身于两家必争之地。则将何以合吴之援而敌魏之强哉。终必失之而两敌傍伺。亦无暇于取益州矣。昭烈知之。故弃不取而以不忍之语。假买人情也。当时关张诸人皆不知。而独孔明知之。故始虽一劝而终不更劝也。说者谓温公以姓司马故为晋而与魏摈蜀。此俗论也。温公岂有是哉。特识见未到耳。温公之意。盖以魏实受汉禅。晋实代魏而为天子。一隅之蜀。既非献帝之亲子亲弟。则不可以蜀之故而不以正统与晋也。却不知蜀虽绍汉而不害于晋之为正统矣。然其心尚有不安。故以南唐之说文之。夫南唐何可与蜀比。南唐起于唐室既亡之久。而全忠,存勖。皆是夷狄之种。则当时人心之思唐。亦如新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1H 页
 莽之时。人之思汉。故冒称伪系。假此以欺人耳。若昭烈则明明是景帝之后。而又于献帝逊位之年。发丧制服。建号于蜀。则其义理光明正大。无纤毫可疑矣。果如南唐之冒称伪系。则孔明何以帝胄之说。一称之于草庐初见之日。再称之于江东求救之日。而王朗之见骂。曹丕之见讨也。彼何无一言以破之也。司马公之言。不难辨矣。以此知凡事之外虽似然而心所不安者。皆非义理之正也。
莽之时。人之思汉。故冒称伪系。假此以欺人耳。若昭烈则明明是景帝之后。而又于献帝逊位之年。发丧制服。建号于蜀。则其义理光明正大。无纤毫可疑矣。果如南唐之冒称伪系。则孔明何以帝胄之说。一称之于草庐初见之日。再称之于江东求救之日。而王朗之见骂。曹丕之见讨也。彼何无一言以破之也。司马公之言。不难辨矣。以此知凡事之外虽似然而心所不安者。皆非义理之正也。伊川之不吊温公。朱子疑之。而退溪则以为当然。盖若是亲戚之丧。吊不可踰日者。则岂以是为拘。而此则不然。明日亦可。又明日亦可。何必于一日之内。既贺旋吊。使哀庆相杂乎。但恐不必引歌哭之说以起争端也。至于立端中则诚有可疑者。抑兄亡弟及。为宋世时王之制而然耶。夫岂不义而伊川为之哉。此正马肝之论也。
朱子以爱说史学主张时变病东莱。而东莱书中。每先经而后史。尊经而抑史。至于博议等篇。自以为少年场屋所作。深误学者。累累告诫于门人。不知朱子何故如此极言。尝窃疑之。及见语录所论张温,灌夫,盖宽饶等事。不免谋利计功之意。宜朱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1L 页
 子之力救而救其弊也。
子之力救而救其弊也。读南轩集。可以想见其人。表里洞澈。无纤毫渣滓。尽是明道地位人。朱子差有豪气。东坡则又别。
续纲目云程某与苏轼交恶。交恶二字。何可用之于此处乎。且伊川何尝恶东坡。于此可见皇明陆学之盛。而不专尚程朱也。
长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四者之修。何待暇日。东莱以修为讲贯。此语似然。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程子以以直为句。朱子以至刚为句。以直属下句。则刚大二字。形容浩气。犹似欠偏。又与下文无害字意似叠。程子之说恐胜。恨不得面质之也。
无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下馁字分明是气馁。观上有集字下无是字可见。明翁云俱是体馁。恐未然。
惟尧则之。孟子集注训则为法。论语集注训则为准。法与准固是同义。而准又兼平义。以此赞尧与天为一之德。尤衬切。抑以集注之成有先后。而不及改孟子欤。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2H 页
 上则先理而后气。下则先气而后理。理气果有先后之可言乎。理无无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固无先后之可言。而气之所以然者理。则必竟是先有理而后有气。观以字与亦字可见。
上则先理而后气。下则先气而后理。理气果有先后之可言乎。理无无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固无先后之可言。而气之所以然者理。则必竟是先有理而后有气。观以字与亦字可见。慎其独也。陈潜室以必字有无。为教学之异。其说太巧。又非本义。慎独是儒者没身工夫。岂有教学之异。盖中庸则上节戒惧。已包了慎独意。故无必字。大学则以小人之閒居不善。如见肺肝为戒。而极言独之不可不慎。故有必字。
好学近乎知云云。好学与学知相似。力行与勉行相似。而谓之近者何也。盖好学未及乎知而求所以知也。力行未及乎行而求所以行也。知耻耻其不知不行而欲知欲行也。故曰近。
自诚明以下。间章言天道人道。而下有三章连言者。此非偶然。岂照应上篇费之大小之连言三章而然欤。
絜矩语类所录。有以矩絜之。絜之使矩之不同。故后来学者各守一说。不能相通。然其义当以章句为定。章句矩字之训。只曰所以为方。而无之器二字。与论孟诸处矩字之训不同。盖只取其方意而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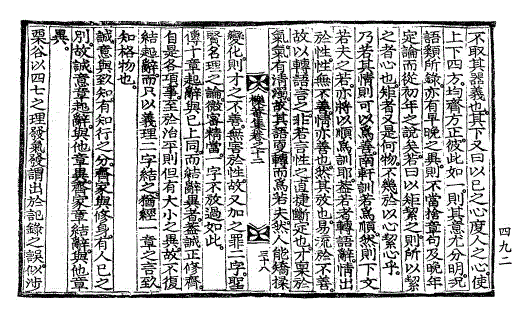 不取其器义也。其下又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彼此如一。则其意尤分明。况语类所录。亦有早晚之异。则不当舍章句及晚年定论而从初年之说矣。若曰以矩絜之。则所以絜之者心也。矩者又是何物。不几于以心絜心乎。
不取其器义也。其下又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彼此如一。则其意尤分明。况语类所录。亦有早晚之异。则不当舍章句及晚年定论而从初年之说矣。若曰以矩絜之。则所以絜之者心也。矩者又是何物。不几于以心絜心乎。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南轩训若为顺。然则下文若夫之若。亦将以顺为训耶。盖若者转语辞。情出于性。性无不善。情亦善也。然其放也。易流于不善。故以转语言之。非若言性之直捷断定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故其语更转而为若夫。然人能矫揉变化。则才之不善。无害于性。故又加之罪二字。圣贤名理之论。微密精当。一字不放过如此。
传十章起辞与已上同。而结辞异者。盖诚正修齐。自是各项事。至于治平则但有大小之异。故不复结起辞。而只以义理二字结之。犹经一章之言致知格物也。
诚意与致知。有知行之分。齐家与修身。有人己之别。故诚意章起辞。与他章异。齐家章结辞。与他章异。
栗谷以四七之理发气发谓出于记录之误。似涉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3H 页
 过当。四七虽同是一情。而名目既异。则四端只可谓之四端而不可谓七情也。七情只可谓之七情而不可谓四端也。四端既剔出善一边而谓之理发。则七情之兼理气者。独不可对四端而谓之气发乎。四端之理发。非无气而理自发也。七情之气发。非无理而气专发也。各就其重者而言之耳。大抵名利之说。分开处当分开说。浑沦处当浑沦说。四七则当分开说者也。若以分开斥浑沦。浑沦攻分开。则无处不窒碍矣。但退溪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说。似拖引太长。而互发二字。有二情之嫌。未知何如耳。
过当。四七虽同是一情。而名目既异。则四端只可谓之四端而不可谓七情也。七情只可谓之七情而不可谓四端也。四端既剔出善一边而谓之理发。则七情之兼理气者。独不可对四端而谓之气发乎。四端之理发。非无气而理自发也。七情之气发。非无理而气专发也。各就其重者而言之耳。大抵名利之说。分开处当分开说。浑沦处当浑沦说。四七则当分开说者也。若以分开斥浑沦。浑沦攻分开。则无处不窒碍矣。但退溪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说。似拖引太长。而互发二字。有二情之嫌。未知何如耳。己庚礼讼时。怀川以不贰斩之说争之。若只曰贾疏不云长子而云第一子。则或是死于殇年。不为服斩未可知。必得死而服斩之明文然后。可行三年之丧云尔。则两家之说。皆有所据。此讼真未易决也。惜乎后来体而不正。十二斩。檀弓免子游衰。不害为庶子等说。援比过当。专出于务胜愤怼。此所以终自陷于不韪之罪而不得辞欤。
己庚礼讼时。怀川以十二斩之说。證不二斩之义。而许尹诸人之辨。亦无明白劈破者。夫为长子斩。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3L 页
 又为众子斩。则是真二斩也。众子为长子而斩。则皆为长子也。不但十二斩。虽百斩其实一斩也。今有人既为其父斩。而出后于大宗。则所后父死。以前已服斩之故。不为之服斩乎。何以异于是。
又为众子斩。则是真二斩也。众子为长子而斩。则皆为长子也。不但十二斩。虽百斩其实一斩也。今有人既为其父斩。而出后于大宗。则所后父死。以前已服斩之故。不为之服斩乎。何以异于是。四种中以正而不体。不为所后子服斩。此尤春礼说也。明翁宅则以四种之说。以可言之于子孙。而不可言之于父祖。故童土出后而为长子服斩。夫体者父子相传之体也。故四种中称于子而不称于孙。所后子既为己子。何可以不体称之乎。若然则四种中正而不体条。何以只言嫡孙而不言所后子乎。或难之曰正与体无异。庶子为后。既承正统而曰不正。则所后子独不可不以不体言之乎。曰子之言固然矣。庶子有嫡子。而嫡庶之分不可混。故别而言之。所后子果与己子有别乎。必与己子有别然后。此说可通。此所以四种之只言嫡孙而不言所后子也欤。
我东风气狭小。凡干议论。皆涉偏党。至于礼说。亦有彼此。然如承重妇之姑在而从服。黪制人之终二十七月。是皆俟百世而不惑者也。
甲午大丧时。海隐叔父皆于所居厅事。设卓焚香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4H 页
 受服变服。皆仿退翁乙丑丁卯之例。而书堂与山寺皆公厅也。国服之行于私室。未知于义果何如。而虚位之设。尤似未安。恨当时年尚幼。疑之而不能质之也。
受服变服。皆仿退翁乙丑丁卯之例。而书堂与山寺皆公厅也。国服之行于私室。未知于义果何如。而虚位之设。尤似未安。恨当时年尚幼。疑之而不能质之也。众孙妇之缌。终涉于薄。盖古者众子妇之服小功。则众孙妇之服不得不为缌。理固然也。而魏徵既升嫡妇为期。又升众妇为大功。则以次升。嫡孙妇为大功。众孙妇为小功。似于情文惬矣。岂当时偶未之及耶。且其夫则大功。而其妻则缌。似于轻重亦不伦矣。
魏徵升舅之服而同于从母。朱子以为姨舅亲同而服异。殊不可晓。后王有作。变而通之。亦未为过。其意盖以徵降姨之服而同于舅可。升舅之服而同于姨不可也。然窃疑母党之服。因母而生。母党之有从母。似父党之有从父。此所谓以名加者。正圣人制服精微之义也。故升舅之服固不可。而降姨之服亦不可也。
成服后时者变制。明翁以为丧出时丧人既在侧。则与追后闻讣者。义实不同。特成服差退而已。二十七月先王定制。不可过也。似当以丧出日为练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4L 页
 祥。此固揣量事情。曲尽精细之言。然亦有极窒碍处。若或不幸而成服或在七八月八九月之后。或又在练月练后。则齐衰重制。将旋成而旋除乎。又将未受服而直行练乎。此等处不得不以朱子答曾无疑书。为处变之三尺。而不容有别说也。且朱子书中云令兄丧期成服太晚。既失之于前云云。则非指追后闻讣者明矣。岂非后人之所遵用者乎。虽过于二十七月之限。亦不害为虽加一日。犹贤于已也。
祥。此固揣量事情。曲尽精细之言。然亦有极窒碍处。若或不幸而成服或在七八月八九月之后。或又在练月练后。则齐衰重制。将旋成而旋除乎。又将未受服而直行练乎。此等处不得不以朱子答曾无疑书。为处变之三尺。而不容有别说也。且朱子书中云令兄丧期成服太晚。既失之于前云云。则非指追后闻讣者明矣。岂非后人之所遵用者乎。虽过于二十七月之限。亦不害为虽加一日。犹贤于已也。自汉以后。当以昌黎为文宗。柳之记胜于韩而闳淡不足。欧阳之志碣胜于韩而格力不足。善学者当有以辨之。
文至于昌黎。诗至于少陵。而有一定之率。犹礼乐之有周公。圣学之有孔夫子也。
世之为文章者。必曰先秦而韩欧以下吾不为也。若王弇州之类是也。然殊不知文章亦随其风气而变。先秦自先秦。韩欧自韩欧。韩欧且不能为先秦。况韩欧以下乎。是无异于责簠簋笾豆之饰者曰何不为瓦坯之古也。责黼黻絺绣之美者曰何不为毛革之坚也。不知其可也。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5H 页
 今之为文章者。务欲扤隉其句字。奇邪其尺幅。断续其音节。隐暗其意趣。曰此先秦也。然先秦之文。何尝有险棘艰深之态乎。且殷盘周诰之佶屈聱牙。不若二典三谟之和平浑厚也。
今之为文章者。务欲扤隉其句字。奇邪其尺幅。断续其音节。隐暗其意趣。曰此先秦也。然先秦之文。何尝有险棘艰深之态乎。且殷盘周诰之佶屈聱牙。不若二典三谟之和平浑厚也。文章虽小技。而与治教相关。故体制气习。代各不同。观于唐虞三代及战国汉晋唐宋之文可知。我国治教。文过于实。故其文皆气力小而色态胜。宣仁以前。号为钜公者。亦不免桧曹以下尤无讥焉。可叹也已。
文章虽小技。而体制不可混。如序不可以为记。传不可以为序。以至铭颂识跋。莫不皆然。韩柳之文。分明可别。欧苏以下。或不免时有杂用处。尽乎造其极臻其妙哉。虽小技亦难也。
文章有轨范。而轨范与蹈袭不同。如平铺者为序。错落者为记。恳到者为书。声响者为颂。劄着者为铭。真切者为箴。谨严者为传。精简者为跋。合序与记者为行状。合传与跋者为志碣。铺置宜大。援證宜实。照应宜错。结束宜紧。此轨范也。出乎此则非所谓文也。若夫引而伸之。操纵舒缩。变化无方者。存乎其人。然要之去陈而生新。尚淡而斥奇。敛华
栎庵集卷之十二 第 495L 页
 而就实。始可与语文章之妙矣。
而就实。始可与语文章之妙矣。大抵作文之法。闳深典雅者其本也。风神滋汁者其外也。二者俱不可偏废。然必有其本而后。形于外者愈益出色。譬如作屋。必基址牢固。材木坚实。然后砻斲丹雘。皆有所施。今之所谓风神者。皆虚影也。所谓滋汁者。乃腐臭也。
我东文章。当以牧隐为首。本朝则毕斋象村为巨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