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杂著
杂著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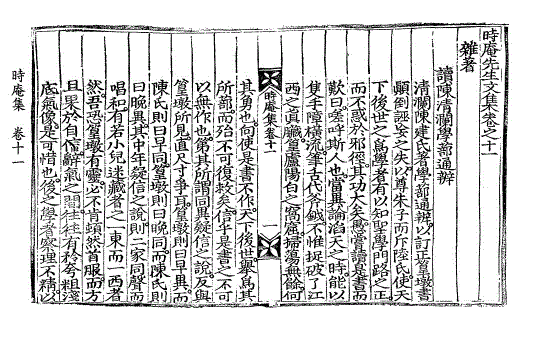 读陈清澜学蔀通辨
读陈清澜学蔀通辨清澜陈建氏著学蔀通辨。以订正篁墩书颠倒诬妄之失。以尊朱子而斥陆氏。使天下后世之为学者有以知圣学门路之正。而不惑于邪径。其功大矣。愚尝读是书而叹曰。嗟呼斯人也。当异论滔天之时。能以只手障横流。笔舌代斧钺。不惟捉破了江西之真脏。篁庐阳白之窝窟。扫荡无馀。何其勇也。向使是书不作。天下后世。举为其所蔀。而殆不可复救矣。信乎是书之不可以无作也。第其所谓同异疑信之说。反与篁墩所见。直尺寸争耳。篁墩则曰早异。而陈氏则曰早同。篁墩则曰晚同。而陈氏则曰晚异。其中年疑信之说。则二家同声而唱和。有若小儿迷藏者之一东而一西者然。吾恐篁墩有灵。必不肯顿然首服。而方且果于自信。辞气之间。往往有矜夸粗浅底气像。是可惜也。后之学者察理不精。以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5L 页
 为是尊朱斥陆之书。并与其误处而一直尊信。则岂不大可惧也哉。于是不揆瞽陋。略加条辨如左。
为是尊朱斥陆之书。并与其误处而一直尊信。则岂不大可惧也哉。于是不揆瞽陋。略加条辨如左。癸酉绍兴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岁。赴任同安主簿。始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之门。年谱云初朱子学靡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自云初见延平。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公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会不下。道亦无他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便自见得。某后来方晓得他说。朱子语类云佛学旧尝参究。后颇疑其不是。及见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会学问看如何。后年岁间。渐见其非。
陈氏曰。朱子早年之学。大略如此。后十年。延平方卒。
愚按年谱曰初先生学靡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者。亦既有年。及见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尽能掊击其失。又记先生尝言曰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又记延平与罗博文书曰。元晦进学甚力。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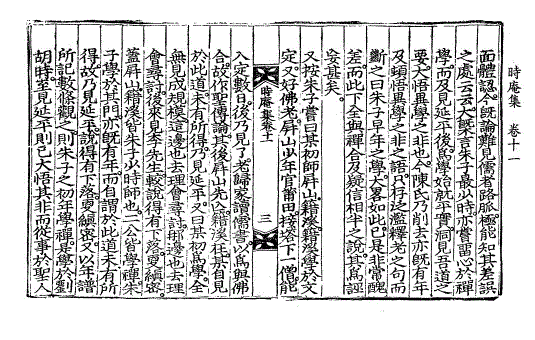 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知其差误之处云云。大槩言朱子最少时。亦尝留心于禅学。而及见延平后。为学始就平实。洞见吾道之要。大悟异学之非也。今陈氏乃削去亦既有年及顿悟异学之非之语。只存泛滥释老之句而断之曰朱子早年之学。大略如此。已是非常丑差。而此下全与禅合及疑信相半之说。其为诬妄甚矣。
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知其差误之处云云。大槩言朱子最少时。亦尝留心于禅学。而及见延平后。为学始就平实。洞见吾道之要。大悟异学之非也。今陈氏乃削去亦既有年及顿悟异学之非之语。只存泛滥释老之句而断之曰朱子早年之学。大略如此。已是非常丑差。而此下全与禅合及疑信相半之说。其为诬妄甚矣。又按朱子尝曰某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屏山少年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又曰某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盖屏山,籍溪皆朱子少时师也。二公皆学禅。朱子学于其门。亦既有年。而自谓于此道未有所得。故乃见延平。说得有下落。更缜密。又以年谱所记数条观之。则朱子之初年学禅。是学于刘胡时。至见延平则已大悟其非而从事于圣人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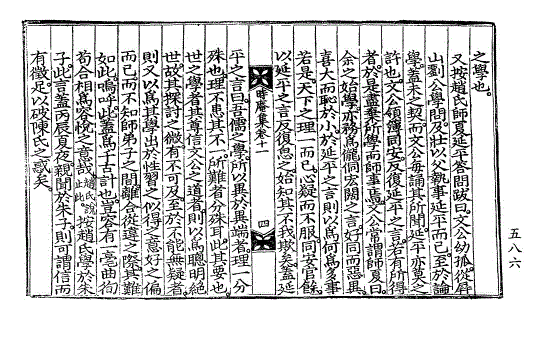 之学也。
之学也。又按赵氏师夏延平答问跋曰。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文公常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儱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馀。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世之学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则以为聪明绝世。故其探讨之微。有不可及。至于不能无疑者。则又以为其学出于性习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师弟子之间。离合从违之际。其难如此。呜呼。此盖为千古计也。岂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为容悦之意哉。(赵氏说止此。)按赵氏学于朱子。此言盖丙辰夏夜。亲闻于朱子。则可谓信而有徵。足以破陈氏之惑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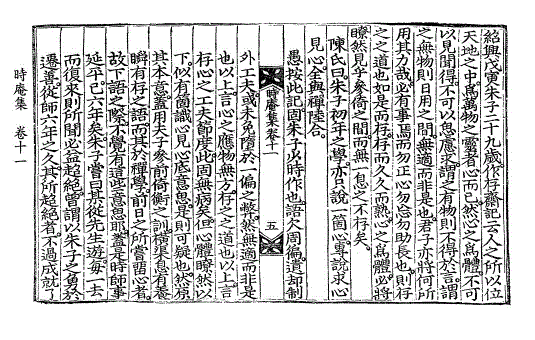 绍兴戊寅朱子二十九岁。作存斋记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然心之为体。不可以见闻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则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必将瞭然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
绍兴戊寅朱子二十九岁。作存斋记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然心之为体。不可以见闻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则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必将瞭然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陈氏曰。朱子初年之学。亦只说一个心。专说求心见心。全与禅陆合。
愚按此记。固朱子少时作也。语欠周遍。遗却制外工夫。或未免堕于一偏之弊。然无适而非是也以上。言心之应物无方。存之之道也以上。言存心之工夫节度。此固无病矣。但心体瞭然以下。似有个识心见心底意思。是则可疑也。然原其本意。盖用夫子参前倚衡之训。横渠息有养瞬有存之语。而其于禅学。前日之所尝留心者。故下语之际。不觉有这些意思耶。盖是时师事延平。已六年矣。朱子尝曰某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曾谓以朱子之勇于迁善。从师六年之久。其所超绝者。不过成就了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7L 页
 全与陆禅合底道理耶。且其自谓为学始就平实。乃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之语。及回头看释氏书。渐渐破绽罅漏百出之言。皆不可信耶。陈氏之说。不足多辨。
全与陆禅合底道理耶。且其自谓为学始就平实。乃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之语。及回头看释氏书。渐渐破绽罅漏百出之言。皆不可信耶。陈氏之说。不足多辨。又按绍兴己卯朱子三十岁。著上蔡语录序。有曰吴中板本。或失本旨。杂他书至诋程氏以助佛学。皆荒浪无根。意近世学佛者私窃为之。以亢其学。绍兴壬午朱子三十三岁。其应诏封事。有曰帝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夫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隆兴癸未朱子三十四岁。入对垂拱殿。其略曰大学之道。本于格物。格物者穷理之谓也。谓之理则无形而难知。谓之物则有迹而易睹。必因物求理。使瞭然无毫发之差。则应事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其著论语训蒙口义序。有曰毋牵于俗学而绝之以为迂且淡也。毋惑于异端而躐之以为近且卑也。杂学辨。是朱子三十三四岁作。而其指斥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之失。明切痛快。所谓阳儒而阴释。其离合出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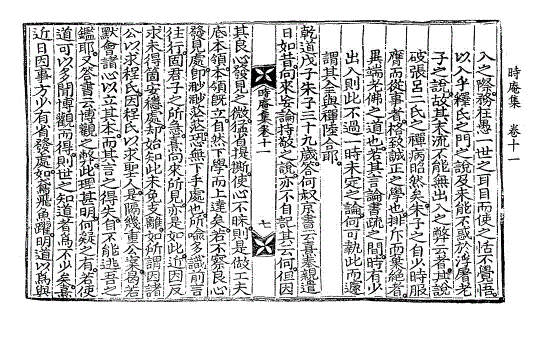 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之说及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云者。其说破张吕二氏之禅病昭然矣。朱子之自少时服膺而从事者。格致诚正之学也。排斥而弃绝者。异端老佛之道也。若其言论书疏之间。时有少出入则此不过一时未定之论。何可执此而遽谓其全与禅陆合耶。
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之说及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云者。其说破张吕二氏之禅病昭然矣。朱子之自少时服膺而从事者。格致诚正之学也。排斥而弃绝者。异端老佛之道也。若其言论书疏之间。时有少出入则此不过一时未定之论。何可执此而遽谓其全与禅陆合耶。乾道戊子朱子三十九岁。答何叔京书云熹奉亲遣日如昔。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所喻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如所谓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几重公案。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耶。又答书云博观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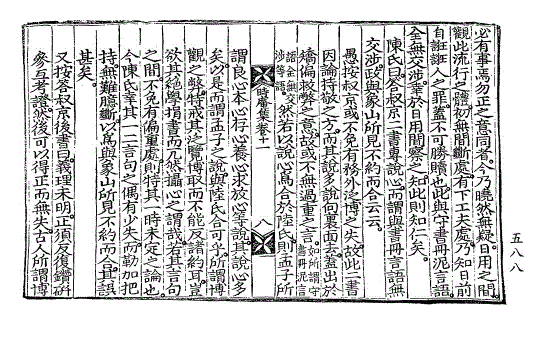 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
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陈氏曰。答叔京二书专说心。而谓与书册言语无交涉。政与象山所见不约而合云云。
愚按叔京或不免有务外泛博之失。故此二书因论持敬之方。而其说多说向里面去。盖出于矫偏救弊之意。故或不无过重之言。(如所谓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等语。)然若以说心为合于陆氏。则孟子所谓良心本心存心养心求放心等说。其说心多矣。以是而谓孟子之说。与陆氏合可乎。所谓博观之弊。特戒其泛览博取而不能反诸约耳。岂欲其绝学捐书而兀然摄心之谓哉。若其言句之间。不免有偏重处。则特其一时未定之论也。今陈氏幸其一二言句之偶有少失。而勒加把持。无难臆断。以为与象山所见不约而合。其误甚矣。
又按答叔京后书曰。义理未明。正须反复钻研参互考證。然后可以得正而无失。古人所谓博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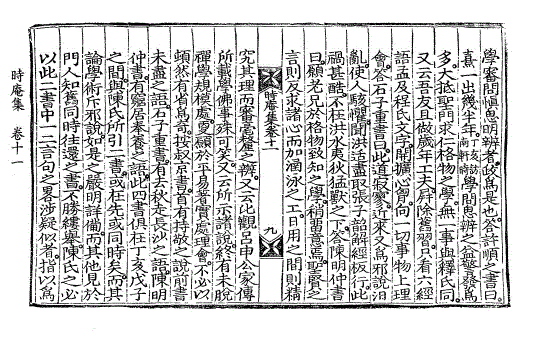 学审问慎思明辨者。政为是也。答许顺之书曰。熹一出几半年。(丁亥访南轩时。)学问思辨之益警发为多。大抵圣门求仁格物之学。无一事与释氏同。又云吾友且做岁年工夫。屏除旧习。只看六经语孟及程氏文字。开扩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会。答石子重书曰。此道寂寥。近来又为邪说汩乱。使人骇惧。闻洪适尽取张子韶解经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答陈明仲书曰。愿老兄于格物致知之学。稍留意焉。圣贤之言则反求诸心而加涵泳之工。日用之间则精究其理而审毫釐之辨。又云比观吕申公家传所载学佛事殊可笑。又云所示诸说。终有未脱禅学规模处。更愿于平易著实处理会。不必以顿然有省为奇。按叔京书。首有持敬之说前书未尽之语。石子重书。有去秋走长沙之语。陈明仲书。有穷居奉养之语。此四书俱在丁亥戊子之间。与陈氏所引二书。或在先或同时矣。而其论学术斥邪说。如是之严明详备。而其他见于门人知旧同时往还之书。不胜缕举。陈氏之必以此二书中一二言句之略涉疑似者。指以为
学审问慎思明辨者。政为是也。答许顺之书曰。熹一出几半年。(丁亥访南轩时。)学问思辨之益警发为多。大抵圣门求仁格物之学。无一事与释氏同。又云吾友且做岁年工夫。屏除旧习。只看六经语孟及程氏文字。开扩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会。答石子重书曰。此道寂寥。近来又为邪说汩乱。使人骇惧。闻洪适尽取张子韶解经板行。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答陈明仲书曰。愿老兄于格物致知之学。稍留意焉。圣贤之言则反求诸心而加涵泳之工。日用之间则精究其理而审毫釐之辨。又云比观吕申公家传所载学佛事殊可笑。又云所示诸说。终有未脱禅学规模处。更愿于平易著实处理会。不必以顿然有省为奇。按叔京书。首有持敬之说前书未尽之语。石子重书。有去秋走长沙之语。陈明仲书。有穷居奉养之语。此四书俱在丁亥戊子之间。与陈氏所引二书。或在先或同时矣。而其论学术斥邪说。如是之严明详备。而其他见于门人知旧同时往还之书。不胜缕举。陈氏之必以此二书中一二言句之略涉疑似者。指以为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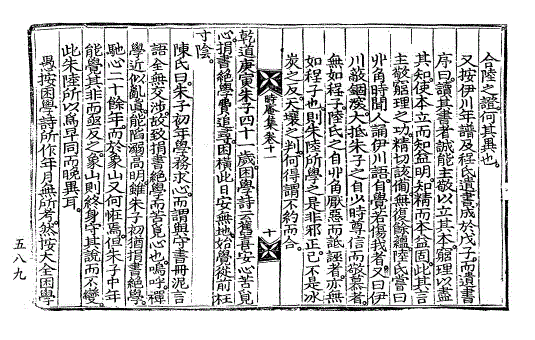 合陆之證。何其异也。
合陆之證。何其异也。又按伊川年谱及程氏遗书成于戊子。而遗书序曰。读其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尽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此其言主敬穷理之功。精切该备。无复馀蕴。陆氏尝曰丱角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蔽锢深。大抵朱子之自少时尊信而敬慕者。无如程子。陆氏之自丱角厌恶而诋诬者。亦无如程子也。则朱陆所学之是非邪正。已不是冰炭之反。天壤之判。何得谓不约而合。
乾道庚寅朱子四十一岁。困学诗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横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陈氏曰。朱子初年学务求心。而谓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故致捐书绝学而苦觅心也。呜呼。禅学近似乱真。能陷溺高明。虽朱子初犹捐书绝学。驰心二十馀年。而于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觉其非而亟反之。象山则终身守其说而不变。此朱陆所以为早同而晚异耳。
愚按困学诗所作年月无所考。然按大全困学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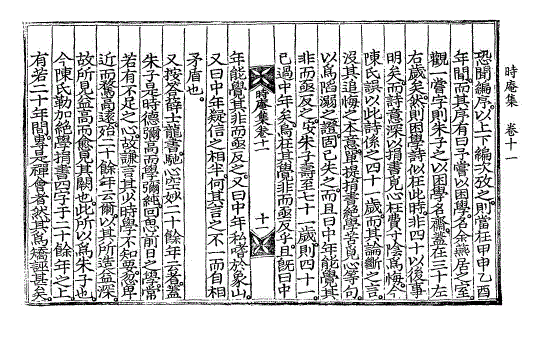 恐闻编序。以上下编次考之。则当在甲申乙酉年间。而其序有曰予尝以困学。名余燕居之室。观一尝字则朱子之以困学名斋。盖在三十左右岁矣。然则困学诗似在此时。非四十以后事明矣。而诗意深以捐书觅心枉费寸阴为悔。今陈氏误以此诗系之四十一岁。而其论断之言。没其追悔之本意。单提捐书绝学苦觅心等句。以为陷溺之證。固已失之。而且曰中年能觉其非而亟反之。按朱子寿至七十一岁。则四十一。已过中年矣。乌在其觉非而亟反乎。且既曰中年能觉其非而亟反之。又曰中年私嗜于象山。又曰中年疑信之相半。何其言之不一而自相矛盾也。
恐闻编序。以上下编次考之。则当在甲申乙酉年间。而其序有曰予尝以困学。名余燕居之室。观一尝字则朱子之以困学名斋。盖在三十左右岁矣。然则困学诗似在此时。非四十以后事明矣。而诗意深以捐书觅心枉费寸阴为悔。今陈氏误以此诗系之四十一岁。而其论断之言。没其追悔之本意。单提捐书绝学苦觅心等句。以为陷溺之證。固已失之。而且曰中年能觉其非而亟反之。按朱子寿至七十一岁。则四十一。已过中年矣。乌在其觉非而亟反乎。且既曰中年能觉其非而亟反之。又曰中年私嗜于象山。又曰中年疑信之相半。何其言之不一而自相矛盾也。又按答薛士龙书。驰心空妙二十馀年云者。盖朱子是时德弥高而学弥纯。回思前日之学。常若有不足之心。故谦言其少时学不知要。忽卑近而骛高远。殆二十馀年云尔。以其所造益深。故所见益高而愈见其阙也。此所以为朱子也。今陈氏勒加绝学捐书四字于二十馀年之上。有若二十年间。专是禅会者然。其为矫诬甚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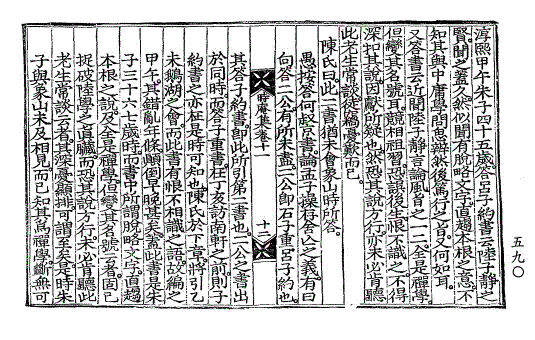 淳熙甲午朱子四十五岁。答吕子约书云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何如耳。
淳熙甲午朱子四十五岁。答吕子约书云陆子静之贤。闻之盖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何如耳。又答书云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然恐其说方行。亦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徒窃忧叹而已。
陈氏曰。此二书犹未会象山时所答。
愚按答何叔京书。论孟子操存舍亡之义。有曰向答二公。有所未尽。二公即石子重,吕子约也。其答子约书。即此所引第二书也。二公之书出于同时。而答子重书。在丁亥访南轩之前。则子约书之亦在是时可知也。陈氏于下章。将引乙未鹅湖之会。而此书有恨不相识之语。故编之甲午。其错乱年条。颠倒早晚甚矣。盖此书是朱子三十六七岁时。而书中所谓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说。及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云者。固已捉破陆学之真脏。而恐其说方行。未必肯听此老生常谈云者。其深忧显排。可谓至矣。是时朱子与象山未及相见。而已知其为禅学。断无可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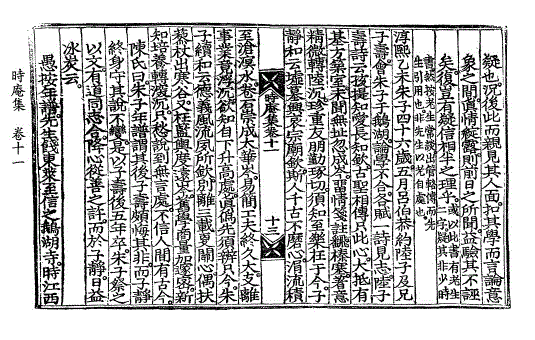 疑也。况后此而亲见其人面。扣其学而言论意象之间。真情绽露。则前日之所闻。益验其不诬矣。复岂有疑信相半之理乎。(或以此书有老生二字。疑其非少时书。然按老生常谈。出管辂传而先生引用也。非先生以老自处也。)
疑也。况后此而亲见其人面。扣其学而言论意象之间。真情绽露。则前日之所闻。益验其不诬矣。复岂有疑信相半之理乎。(或以此书有老生二字。疑其非少时书。然按老生常谈。出管辂传而先生引用也。非先生以老自处也。)淳熙乙未朱子四十六岁。五月吕伯恭约陆子及兄子寿。会朱子于鹅湖。论学不合。各赋一诗见志。陆子寿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笺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子静和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卷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朱子续和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陈氏曰。朱子年谱谓其后子寿颇悔其非。而子静终身守其说不变。是以子寿后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同志合。降心从善之许。而于子静。日益冰炭云。
愚按年谱。先生饯东莱至信之鹅湖寺。时江西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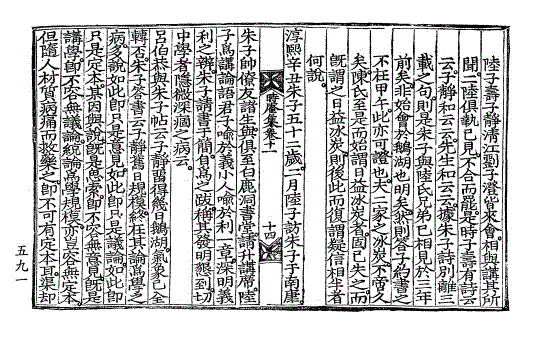 陆子寿子静清江刘子澄皆来会。相与讲其所闻。二陆俱执己见。不合而罢。是时子寿有诗云云。子静和云云。先生和云云。据朱子诗别离三载之句。则是朱子与陆氏兄弟已相见于三年前矣。非始会于鹅湖也明矣。然则答子约书之不在甲午。此亦可證也。夫二家之冰炭。不啻久矣。陈氏至是而始谓日益冰炭者。固已失之。而既谓之日益冰炭。则后此而复谓疑信相半者何说。
陆子寿子静清江刘子澄皆来会。相与讲其所闻。二陆俱执己见。不合而罢。是时子寿有诗云云。子静和云云。先生和云云。据朱子诗别离三载之句。则是朱子与陆氏兄弟已相见于三年前矣。非始会于鹅湖也明矣。然则答子约书之不在甲午。此亦可證也。夫二家之冰炭。不啻久矣。陈氏至是而始谓日益冰炭者。固已失之。而既谓之日益冰炭。则后此而复谓疑信相半者何说。淳熙辛丑朱子五十二岁。二月陆子访朱子于南康。朱子帅僚友诸生。与俱至白鹿洞书堂。请升讲席。陆子为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明义利之辨。朱子请书于简。自为之跋。称其发明恳到。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云。
吕伯恭与朱子帖云子静留得几日鹅湖。气象已全转否。朱子答书云子静旧日规模。终在其论为学之病。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与说。既是思索。即不容无意见。既是讲学。即不容无议论。统论为学规模。亦岂容无定本。但随人材质病痛而救药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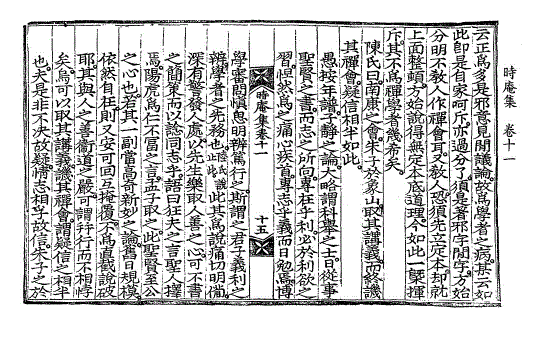 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閒议论。故为学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过分了。须是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
云正为多是邪意见閒议论。故为学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过分了。须是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禅会耳。又教人。恐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挥斥。其不为禅学者几希矣。陈氏曰。南康之会。朱子于象山。取其讲义。而终讥其禅会。疑信相半如此。
愚按年谱。子静之论。大略谓科举之士。日从事圣贤之书。而志之所向。专在乎利。必于利欲之习。怛然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斯谓之君子义利之辨。学者之先务也。(陆氏说止此。)此其为说痛切明备。深有警发人处。以先生乐取人善之心。可不书之简策而以谂同志乎。语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阳虎为仁不富之言。孟子取之。此圣贤至公之心也。若其一副当高奇新妙之论。旧日规模。依然自在。则又安可回互掩覆。不为直截说破耶。其与人之善卫道之严。可谓并行而不相悖矣。乌可以取其讲义。讥其禅会。谓疑信之相半也。夫是非不决故疑。情志相孚故信。朱子之于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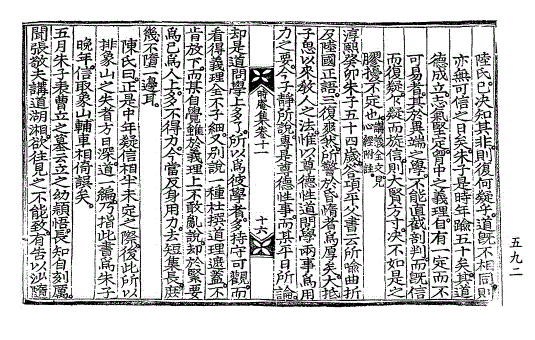 陆氏。已决知其非。则复何疑乎。道既不相同。则亦无可信之日矣。朱子是时年踰五十矣。其道德成立。志气坚定。胸中之义理。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其于异端之学。不能直截剖判。而既信而复疑。乍疑而旋信。则大贤方寸。决不如是之胶扰不定也。(讲义全文。见心经附注。)
陆氏。已决知其非。则复何疑乎。道既不相同。则亦无可信之日矣。朱子是时年踰五十矣。其道德成立。志气坚定。胸中之义理。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其于异端之学。不能直截剖判。而既信而复疑。乍疑而旋信。则大贤方寸。决不如是之胶扰不定也。(讲义全文。见心经附注。)淳熙癸卯朱子五十四岁。答项平父书云所喻曲折及陆国正语。三复爽然。所警于昏惰者为厚矣。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某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
陈氏曰。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际。后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编。乃指此书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辅车相倚误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颖悟。长知自刻厉。闻张敬夫讲道湖湘。欲往见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随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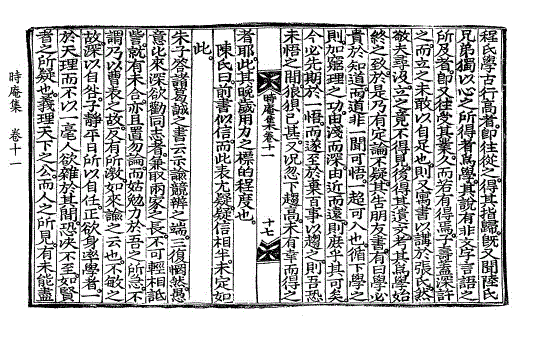 程氏学古行高者。即往从之。得其指归。既又闻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有非文字言语之所及者。即又往受其业。久而若有得焉。子寿盖深许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则又寓书以讲于张氏。然敬夫寻没。立之竟不得见。后得其遗文。考其为学始终之致。于是乃有定论不疑。其告朋友书。有曰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穷理之功。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则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趋之。则吾恐未悟之间。狼狈已甚。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程度也。
程氏学古行高者。即往从之。得其指归。既又闻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有非文字言语之所及者。即又往受其业。久而若有得焉。子寿盖深许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则又寓书以讲于张氏。然敬夫寻没。立之竟不得见。后得其遗文。考其为学始终之致。于是乃有定论不疑。其告朋友书。有曰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穷理之功。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则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趋之。则吾恐未悟之间。狼狈已甚。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程度也。陈氏曰。前书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诸葛诚之书云示谕竞辨之端。三复惘然。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来谕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3L 页
 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少长之序礼逊之容。至今怀不满。
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无复少长之序礼逊之容。至今怀不满。陈氏曰。朱子因门人竞辨之过。故作此书以解之。犹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说也。
淳熙乙巳朱子五十六岁。贻陆子书云奏篇垂寄。得闻至论。慰沃良深。语圆意活。浑浩流转。有以见所养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岭带来耳。
陈氏曰。象山去年冬。上轮对五劄。因录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
愚按项平父书所谓去短集长及诸葛诚之书所谓兼取两家之长之说。皆朱子自谦之辞也。盖是时犹有望于象山。故为此宛转平恕之说。使之潜销其忿怼自私之心。而庶几因此而或有悔悟之萌也。观其所谓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之语。其气象之忠厚宛转。千载之下。亦可使人销其鄙吝之私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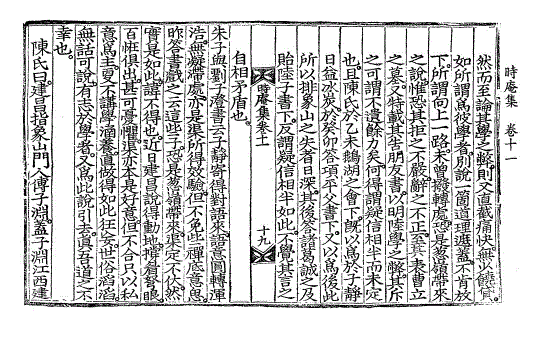 然而至论其学之弊。则又直截痛快。无少饶贷。如所谓为彼学者。别说一个道理遮盖。不肯放下。所谓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恐是葱岭带来之说。惟恐其拒之不严。辞之不正。至其表曹立之墓。又特载其告朋友书。以明陆学之弊。其斥之可谓不遗馀力矣。何得谓疑信相半而未定也。且陈氏于乙未鹅湖之会下。既以为于子静日益冰炭。于癸卯答项平父书下。又以为后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日深。其后答诸葛诚之及贻陆子书下。反谓疑信相半如此。不觉其言之自相矛盾也。
然而至论其学之弊。则又直截痛快。无少饶贷。如所谓为彼学者。别说一个道理遮盖。不肯放下。所谓向上一路。未曾拨转处。恐是葱岭带来之说。惟恐其拒之不严。辞之不正。至其表曹立之墓。又特载其告朋友书。以明陆学之弊。其斥之可谓不遗馀力矣。何得谓疑信相半而未定也。且陈氏于乙未鹅湖之会下。既以为于子静日益冰炭。于癸卯答项平父书下。又以为后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日深。其后答诸葛诚之及贻陆子书下。反谓疑信相半如此。不觉其言之自相矛盾也。朱子与刘子澄书云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但不免些禅底意思。昨答书戏之云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渠定不伏。然实是如此。讳不得也。近日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弩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更不讲学涵养。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于学者。又为此说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陈氏曰。建昌指象山门人傅子渊。盖子渊江西建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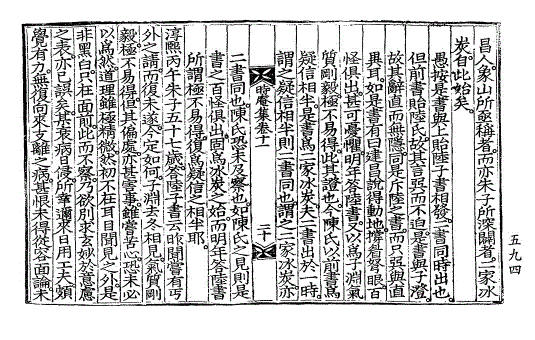 昌人。象山所亟称者。而亦朱子所深辟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
昌人。象山所亟称者。而亦朱子所深辟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愚按是书与上贻陆子书相发。二书同时出也。但前书贻陆氏。故其言巽而不迫。是书与子澄。故其辞直而无隐。同是斥陆之书。而只巽与直异耳。如是书有曰建昌说得动地。撑眉弩眼。百怪俱出。甚可忧惧。明年答陆书。又以为子渊气质刚毅。极不易得。此其證也。今陈氏以前书为疑信相半。是书为二家冰炭。夫二书出于一时。谓之疑信相半则二书同也。谓之二家冰炭。亦二书同也。陈氏恐未及察也。如陈氏之见则是书之百怪俱出。固为冰炭之始。而明年答陆书所谓极不易得。复为疑信之相半耶。
淳熙丙午朱子五十七岁。答陆子书云昨闻尝有丐外之请。而复未遂。今定如何。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但其偏处。亦甚害事。虽尝苦心。恐未必以为然。道理虽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某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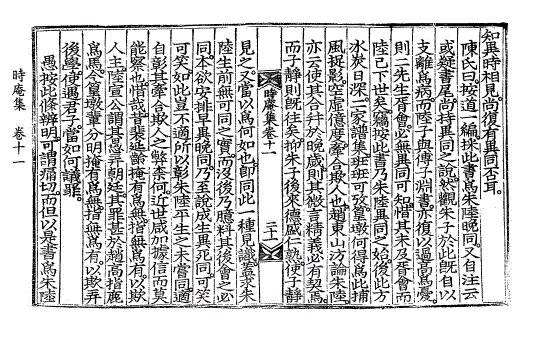 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
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陈氏曰。按道一编。采此书为朱陆晚同。又自注云或疑书尾。尚持异同之说。然观朱子于此既自以支离为病。而陆子与傅子渊书。亦复以过高为忧。则二先生胥会。必无异同可知。惜其未及胥会而陆已下世矣。窃按此书乃朱陆异同之始。后此方冰炭日深。二家谱集。班班可考。篁墩何得为此捕风捉影。空虚亿度。牵合欺人也。赵东山汸论朱陆。亦云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抑朱子后来德盛仁熟。使子静见之。又当以为何如也。即同此一种见识。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后乃臆料其后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柰何。近世咸加据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宣公谓其愚弄朝廷。其罪甚于赵高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后学。使遇君子。当如何议罪。
愚按此条辨明。可谓痛切。而但以是书为朱陆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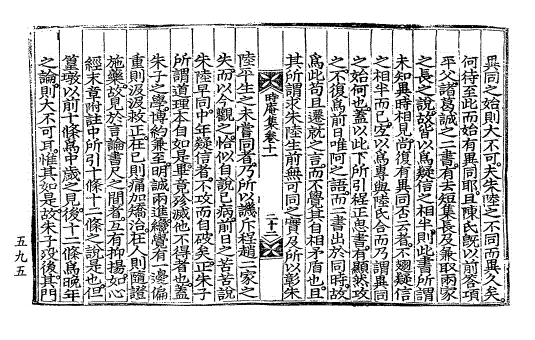 异同之始则大不可。夫朱陆之不同而异久矣。何待至此而始有异同耶。且陈氏既以前答项平父,诸葛诚之二书。有去短集长及兼取两家之长之说。故皆以为疑信之相半。则此书所谓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云者。不翅疑信之相半而已。宜以为专与陆氏合而乃谓异同之始何也。盖以此下所引程正思书。有显然攻之。不复为前日唯阿之语。而二书出于同时。故为此苟且迁就之言。而不觉其自相矛盾也。且其所谓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及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者。乃所以讥斥程赵二家之失。而以今观之。恰似自说己病。前日之苦苦说朱陆早同。中年疑信者。不攻而自破矣。正朱子所谓道理本自如是。毕竟殄灭他不得者也。盖朱子之学。博约兼至。明诚两进。才觉有一边偏重则汲汲救正。在己则痛加矫治。在人则随證施药。故见于言论书尺之间者。互有抑扬。如心经末章附注中所引十条十二条之说是也。但篁墩以前十条为中岁之见。后十二条为晚年之论。则大不可耳。惟其如是。故朱子殁后。其门
异同之始则大不可。夫朱陆之不同而异久矣。何待至此而始有异同耶。且陈氏既以前答项平父,诸葛诚之二书。有去短集长及兼取两家之长之说。故皆以为疑信之相半。则此书所谓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云者。不翅疑信之相半而已。宜以为专与陆氏合而乃谓异同之始何也。盖以此下所引程正思书。有显然攻之。不复为前日唯阿之语。而二书出于同时。故为此苟且迁就之言。而不觉其自相矛盾也。且其所谓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及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者。乃所以讥斥程赵二家之失。而以今观之。恰似自说己病。前日之苦苦说朱陆早同。中年疑信者。不攻而自破矣。正朱子所谓道理本自如是。毕竟殄灭他不得者也。盖朱子之学。博约兼至。明诚两进。才觉有一边偏重则汲汲救正。在己则痛加矫治。在人则随證施药。故见于言论书尺之间者。互有抑扬。如心经末章附注中所引十条十二条之说是也。但篁墩以前十条为中岁之见。后十二条为晚年之论。则大不可耳。惟其如是。故朱子殁后。其门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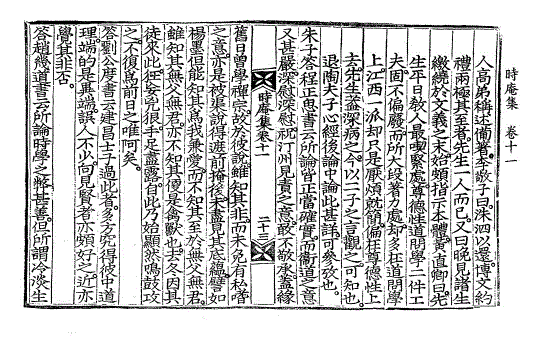 人高弟称述备著。李敬子曰。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晚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末。始颇指示本体。黄直卿曰。先生平日教人最吃紧处。尊德性道问学二件工夫。固不偏废。而所大段著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厌烦就简。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盖深病之。今以二子之言观之。可知也。退陶夫子心经后论中论此甚详。可参考也。
人高弟称述备著。李敬子曰。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晚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末。始颇指示本体。黄直卿曰。先生平日教人最吃紧处。尊德性道问学二件工夫。固不偏废。而所大段著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厌烦就简。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盖深病之。今以二子之言观之。可知也。退陶夫子心经后论中论此甚详。可参考也。朱子答程正思书云所论皆正当确实。而卫道之意又甚严。深慰深慰。祝汀州见责之意。敢不敬承。盖缘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说。虽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譬如杨墨但能知其为我兼爱。而不知其至于无父无君。虽知其无父无君。亦不知其便是禽兽也。去冬因其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自此乃始显然鸣鼓攻之。不复为前日之唯阿矣。
答刘公度书云建昌士子过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异端。误人不少。向见贤者亦颇好之。近亦觉其非否。
答赵几道书云所论时学之弊甚善。但所谓冷淡生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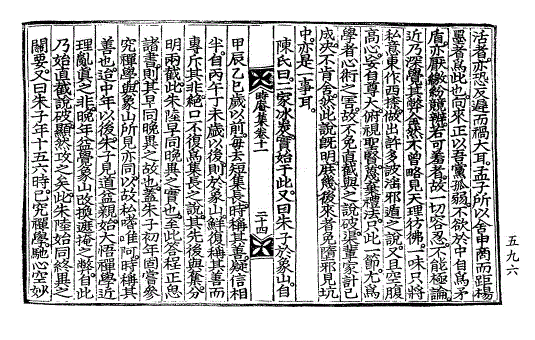 活者。亦恐反迟而祸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杨墨者为此也。向来正以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亦厌缴纷竞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极论。近乃深觉其弊全然不曾略见天理彷佛。一味只将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只此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免直截与之说破。渠辈家计已成。决不肯舍。然此说既明。庶几后来者免堕邪见坑中。亦是一事耳。
活者。亦恐反迟而祸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杨墨者为此也。向来正以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亦厌缴纷竞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极论。近乃深觉其弊全然不曾略见天理彷佛。一味只将私意东作西捺。做出许多诐淫邪遁之说。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只此一节。尤为学者心术之害。故不免直截与之说破。渠辈家计已成。决不肯舍。然此说既明。庶几后来者免堕邪见坑中。亦是一事耳。陈氏曰。二家冰炭。实始于此。又曰朱子于象山。自甲辰乙巳岁以前。每去短集长。时称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岁以后。则于象山。鲜复称其善而专斥其非。绝口不复为集长之说。其先后与夺。分明两截。此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也。至此答程正思诸书。则其早同晚异之故也。盖朱子初年固尝参究禅学。与象山所见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时称其善也。迨中年以后。朱子见道益亲。始大悟禅学近理乱真之非。晚年益觉象山改换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说破。显然攻之矣。此朱陆始同终异之关要。又曰朱子年十五六时。已究禅学。驰心空妙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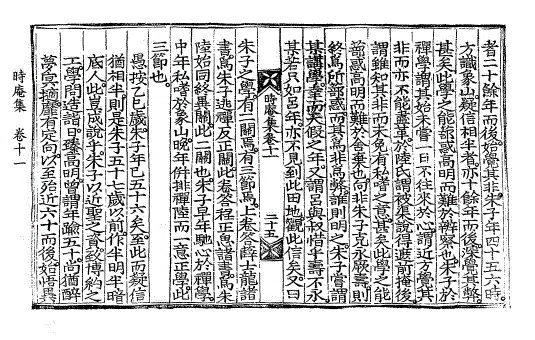 者二十馀年而后。始觉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时。方识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馀年而后。深觉其弊。甚矣此学之能蔀惑高明而难于辨察也。朱子于禅学谓其始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谓近方觉其非而亦不能尽革。于陆氏谓被渠说得遮前掩后。谓虽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甚矣此学之能蔀惑高明而难于舍弃也。向非朱子克永厥寿。则终为所蔀惑。而其为非为弊。谁则明之。朱子尝谓某讲学。幸而天假之年。又谓吕与叔惜乎寿不永。某若只如吕年。亦不见到此田地。观此信矣。又曰朱子之学。有二关焉。有三节焉。上卷答薛士龙诸书。为朱子逃禅反正关。此卷答程正思诸书。为朱陆始同终异关。此二关也。朱子早年驰心于禅学。中年私嗜于象山。晚年并排禅陆而一意正学。此三节也。
者二十馀年而后。始觉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时。方识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馀年而后。深觉其弊。甚矣此学之能蔀惑高明而难于辨察也。朱子于禅学谓其始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谓近方觉其非而亦不能尽革。于陆氏谓被渠说得遮前掩后。谓虽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甚矣此学之能蔀惑高明而难于舍弃也。向非朱子克永厥寿。则终为所蔀惑。而其为非为弊。谁则明之。朱子尝谓某讲学。幸而天假之年。又谓吕与叔惜乎寿不永。某若只如吕年。亦不见到此田地。观此信矣。又曰朱子之学。有二关焉。有三节焉。上卷答薛士龙诸书。为朱子逃禅反正关。此卷答程正思诸书。为朱陆始同终异关。此二关也。朱子早年驰心于禅学。中年私嗜于象山。晚年并排禅陆而一意正学。此三节也。愚按乙巳岁。朱子年已五十六矣。至此而疑信犹相半。则是朱子五十七岁以前。作半明半暗底人。此岂成说乎。朱子以近圣之资。致博约之工。学问造诣。日臻高明。曾谓年踰五十。尚犹醉梦冥擿。靡有定向。以至殆近六十而后。始悟异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7L 页
 学之非耶。陈氏以为向非朱子克永厥寿则终为所蔀惑。噫过矣。朱子谓某讲学。幸而天假之年。此朱子自谦之辞。而因以勉戒学者使不可半涂而废也。孔子尝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假令不幸奠楹之梦。在此数年前。圣人亦不免有大过耶。陈氏又谓答薛士龙诸书。为逃禅反正关。答程正思诸书。为始同终异关。夫陆学即禅学。陆与禅一而二二而一也。逃禅则非陆。同陆则是禅。若逃禅而复归于陆。乌可谓反正乎。薛士龙诸书在朱子四十岁以后。则是朱子四十以前禅学也。程正思诸书在朱子五十七岁以后。则五十七以前陆学也。然则朱子平生所学。专是禅陆。而于圣人之道。终未有闻。其幸而从事于此学。不过自丙午至庚申易箦才十五年而止耳。朱子之为朱子。不亦幸矣乎。陈氏此辨。本欲尊朱子而斥陆氏。其意则善。而此等见解议论。不知其自陷于不韪之罪。可胜惜哉。窃尝推原朱子之意而为之说曰。夫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况以子静之颖悟特达。使其回头改辙。从事于吾儒之学。其成
学之非耶。陈氏以为向非朱子克永厥寿则终为所蔀惑。噫过矣。朱子谓某讲学。幸而天假之年。此朱子自谦之辞。而因以勉戒学者使不可半涂而废也。孔子尝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假令不幸奠楹之梦。在此数年前。圣人亦不免有大过耶。陈氏又谓答薛士龙诸书。为逃禅反正关。答程正思诸书。为始同终异关。夫陆学即禅学。陆与禅一而二二而一也。逃禅则非陆。同陆则是禅。若逃禅而复归于陆。乌可谓反正乎。薛士龙诸书在朱子四十岁以后。则是朱子四十以前禅学也。程正思诸书在朱子五十七岁以后。则五十七以前陆学也。然则朱子平生所学。专是禅陆。而于圣人之道。终未有闻。其幸而从事于此学。不过自丙午至庚申易箦才十五年而止耳。朱子之为朱子。不亦幸矣乎。陈氏此辨。本欲尊朱子而斥陆氏。其意则善。而此等见解议论。不知其自陷于不韪之罪。可胜惜哉。窃尝推原朱子之意而为之说曰。夫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况以子静之颖悟特达。使其回头改辙。从事于吾儒之学。其成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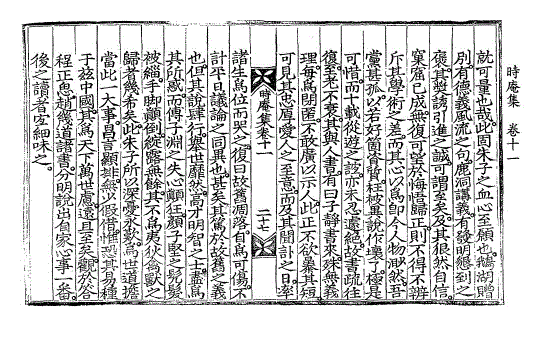 就可量也哉。此固朱子之血心至愿也。鹅湖赠别。有德义风流之句。鹿洞讲义。有发明恳到之褒。其奖诱引进之诚。可谓至矣。及其狠然自信。窠窟已成。无复可望于悔悟归正。则不得不辨斥其学术之差。而其心以为即今人物渺然。吾党甚孤。以若好个资质。枉被异说作坏了。极是可惜。而十载从游之谊。亦未忍遽绝。故书疏往复。至老不衰。其与人书。有曰子静书来。殊无义理。每为闭匿。不敢广以示人。此正不欲㬥其短。可见其忠厚爱人之至意。而及其闻讣之日。率诸生为位而哭之。复曰故旧凋落。自为可伤。不计平日议论之同异也。甚矣。其笃于故旧之义也。但其说肆行。举世靡然。高才明智之士。尽为其所惑。而傅子渊之失心颠狂。颜子坚之髡发被缁。手脚颠倒。绽露无馀。其不为夷狄禽兽之归者几希矣。此朱子所以深忧永叹。为世道担当此一大事。昌言显排。无少假借。惟恐其易种于玆中国。其为天下万世虑。远且至矣。观于答程正思,赵几道诸书。分明说出自家心事一番。后之读者宜细味之。
就可量也哉。此固朱子之血心至愿也。鹅湖赠别。有德义风流之句。鹿洞讲义。有发明恳到之褒。其奖诱引进之诚。可谓至矣。及其狠然自信。窠窟已成。无复可望于悔悟归正。则不得不辨斥其学术之差。而其心以为即今人物渺然。吾党甚孤。以若好个资质。枉被异说作坏了。极是可惜。而十载从游之谊。亦未忍遽绝。故书疏往复。至老不衰。其与人书。有曰子静书来。殊无义理。每为闭匿。不敢广以示人。此正不欲㬥其短。可见其忠厚爱人之至意。而及其闻讣之日。率诸生为位而哭之。复曰故旧凋落。自为可伤。不计平日议论之同异也。甚矣。其笃于故旧之义也。但其说肆行。举世靡然。高才明智之士。尽为其所惑。而傅子渊之失心颠狂。颜子坚之髡发被缁。手脚颠倒。绽露无馀。其不为夷狄禽兽之归者几希矣。此朱子所以深忧永叹。为世道担当此一大事。昌言显排。无少假借。惟恐其易种于玆中国。其为天下万世虑。远且至矣。观于答程正思,赵几道诸书。分明说出自家心事一番。后之读者宜细味之。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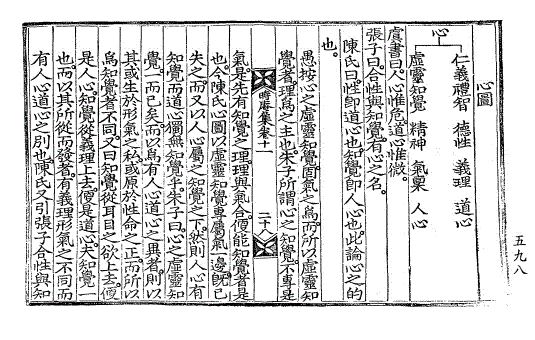 心图
心图삽화 새창열기
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陈氏曰。性即道心也。知觉即人心也。此论心之的也。
愚按心之虚灵知觉。固气之为。而所以虚灵知觉者。理为之主也。朱子所谓心之知觉。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是也。今陈氏心图以虚灵知觉专属气一边。既已失之。而又以人心属之知觉之下。然则人心有知觉而道心独无知觉乎。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又曰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夫知觉一也。而以其所从而发者。有义理形气之不同而有人心道心之别也。陈氏又引张子合性与知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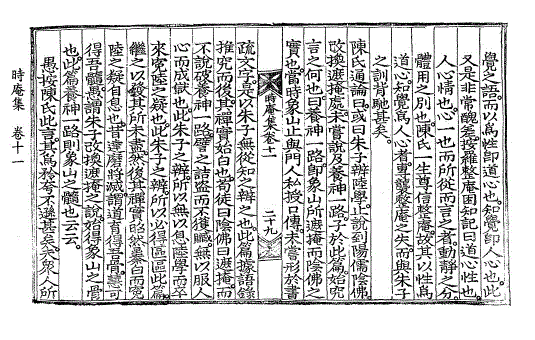 觉之语。而以为性即道心也。知觉即人心也。此又是非常丑差。按罗整庵困知记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所从而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陈氏一生尊信整庵。故其以性为道心。知觉为人心者。专袭整庵之失。而与朱子之训背驰甚矣。
觉之语。而以为性即道心也。知觉即人心也。此又是非常丑差。按罗整庵困知记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所从而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陈氏一生尊信整庵。故其以性为道心。知觉为人心者。专袭整庵之失。而与朱子之训背驰甚矣。陈氏通论曰。或曰朱子辨陆学。止说到阳儒阴佛。改换遮掩处。未尝说及养神一路。子于此篇。始究言之何也。曰养神一路。即象山所遮掩而阴佛之实也。当时象山止与门人私授口传。未尝形于书疏文字。是以朱子无从知之辨之也。此篇据语录推究而后。其禅实始白也。苟徒曰阴佛曰遮掩。而不说破养神一路。譬之诘盗而不获赃。无以服人心而成狱也。此朱子之辨。所以无以息陆学而卒来冤陆之疑也。此朱子之辨。所以必得区区此篇。继之以发其所未尽。然后其禅实昭然㬥白而冤陆之疑自息也。昔达磨将灭。谓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谓朱子改换遮掩之说。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篇养神一路则象山之髓也云云。
愚按陈氏此言。其为矜夸不逊甚矣。夫众人所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5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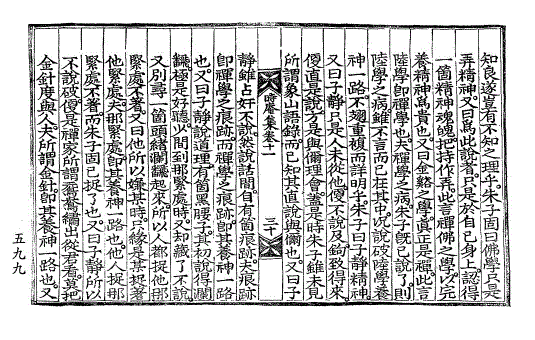 知良遂岂有不知之理乎。朱子固曰佛学只是弄精神。又曰为此说者。只是于自己身上。认得一个精神魂魄。把持作弄。此言禅佛之学。以完养精神为贵也。又曰金溪之学。真正是禅。此言陆学即禅学也。夫禅学之病。朱子既已说了。则陆学之病。虽不言而已在其中。况说破陆学养神一路。不翅重复而详明乎。朱子曰子静精神。又曰子静只是人未从他。便不说及。钩致得来。便直是说。方是与你理会。盖是时朱子虽未见所谓象山语录。而已知其直说与你也。又曰子静虽占奸不说。然说话间。自有个痕迹。夫痕迹即禅学之痕迹。而禅学之痕迹。即其养神一路也。又曰子静说道理。有个黑腰子。其初说得澜翻。极是好听。少间到那紧处时。又却藏了不说。又别寻一个头绪澜翻起来。所以人都捉他那紧处不著。又曰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著他紧处。夫那紧处。即其养神一路也。他人捉那紧处不著。而朱子固已捉了也。又曰子静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䲶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夫所谓金针。即其养神一路也。又
知良遂岂有不知之理乎。朱子固曰佛学只是弄精神。又曰为此说者。只是于自己身上。认得一个精神魂魄。把持作弄。此言禅佛之学。以完养精神为贵也。又曰金溪之学。真正是禅。此言陆学即禅学也。夫禅学之病。朱子既已说了。则陆学之病。虽不言而已在其中。况说破陆学养神一路。不翅重复而详明乎。朱子曰子静精神。又曰子静只是人未从他。便不说及。钩致得来。便直是说。方是与你理会。盖是时朱子虽未见所谓象山语录。而已知其直说与你也。又曰子静虽占奸不说。然说话间。自有个痕迹。夫痕迹即禅学之痕迹。而禅学之痕迹。即其养神一路也。又曰子静说道理。有个黑腰子。其初说得澜翻。极是好听。少间到那紧处时。又却藏了不说。又别寻一个头绪澜翻起来。所以人都捉他那紧处不著。又曰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著他紧处。夫那紧处。即其养神一路也。他人捉那紧处不著。而朱子固已捉了也。又曰子静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䲶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夫所谓金针。即其养神一路也。又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6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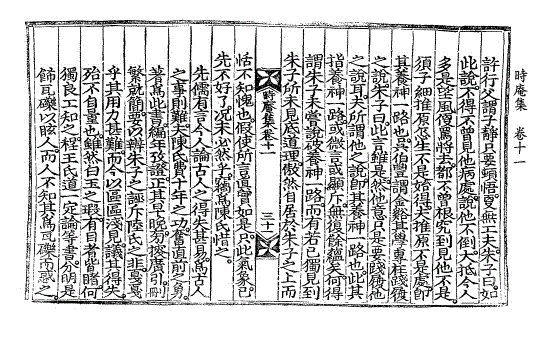 许行父谓子静只要顿悟。更无工夫。朱子曰。如此说。不得不曾见他病处。说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风便骂将去。都不曾根究到见他不是。须子细推原怎生不是始得。夫推原不是处。即其养神一路也。吴伯丰谓金溪其学专在践履之说。朱子曰。此言虽是。然他意只是要践履他之说耳。夫所谓他之说。即其养神一路也。此其指养神一路。或微言或显斥。无复馀蕴矣。何得谓朱子未尝说破养神一路。而有若己独见到朱子所未见底道理。傲然自居于朱子之上而恬不知愧也。假使所言真实如是。只此气象。已先不好了。况未必然乎。窃为陈氏惜之。
许行父谓子静只要顿悟。更无工夫。朱子曰。如此说。不得不曾见他病处。说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风便骂将去。都不曾根究到见他不是。须子细推原怎生不是始得。夫推原不是处。即其养神一路也。吴伯丰谓金溪其学专在践履之说。朱子曰。此言虽是。然他意只是要践履他之说耳。夫所谓他之说。即其养神一路也。此其指养神一路。或微言或显斥。无复馀蕴矣。何得谓朱子未尝说破养神一路。而有若己独见到朱子所未见底道理。傲然自居于朱子之上而恬不知愧也。假使所言真实如是。只此气象。已先不好了。况未必然乎。窃为陈氏惜之。[后书]
先儒有言今人论古人之得失甚易。为古人之事则难。夫陈氏费十年之功。奋直前之勇。著为此书。编年考證。正其早晚。旁搜广引。删繁就简。要以辨朱子之诬斥陆氏之非。戛戛乎其用力甚难。而今以区区浅见。议其得失。殆不自量也。虽然白玉之瑕。有目者皆睹。何独良工知之。程王氏道一定论等书。分明是饰瓦砾以眩人。而人不知其为瓦砾而惑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6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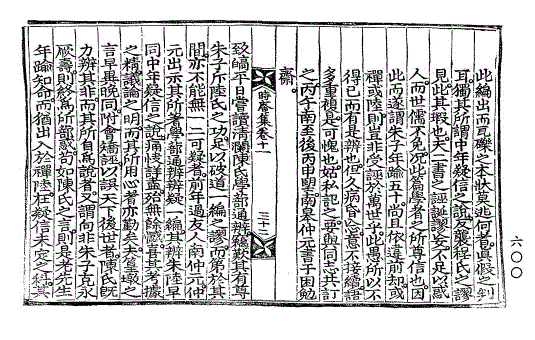 此编出而瓦砾之本状莫逃何者。真假之判耳。独其所谓中年疑信之说。反袭程氏之谬见。此其瑕也。夫二书之诬诞谬妄。不足以惑人。而世儒不免。况此篇学者之所尊信也。因此而遂谓朱子年踰五十。尚且依违前却。或禅或陆。则岂非受诬于万世乎。此愚所以不得已而有是辨也。但久病昏忘。意不接续。语多重复。是可愧也。姑私记之。要与同志共订之。丙午南至后丙申望。南皋仲元书于困勉斋。
此编出而瓦砾之本状莫逃何者。真假之判耳。独其所谓中年疑信之说。反袭程氏之谬见。此其瑕也。夫二书之诬诞谬妄。不足以惑人。而世儒不免。况此篇学者之所尊信也。因此而遂谓朱子年踰五十。尚且依违前却。或禅或陆。则岂非受诬于万世乎。此愚所以不得已而有是辨也。但久病昏忘。意不接续。语多重复。是可愧也。姑私记之。要与同志共订之。丙午南至后丙申望。南皋仲元书于困勉斋。[跋○柳致皓]
致皓平日尝读清澜陈氏学蔀通辨。窃叹其有尊朱子斥陆氏之功。足以破道一编之谬。而第于其间。亦不能无一二可疑者。前年过友人南仲元。仲元出示其所著学蔀通辨辨疑一编。其辨朱陆早同中年疑信之说。痛快详尽。殆无馀憾。喜其考据之精。议论之明。而其所用心者亦勤矣。夫篁墩之言早异晚同。附会矫诬。以误天下后世者。陈氏既力辨其非。而其所自为说者。又谓向非朱子克永厥寿。则终为所蔀惑。苟如陈氏之言。则是老先生年踰知命。而犹出入于禅陆。在疑信未定之科。其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6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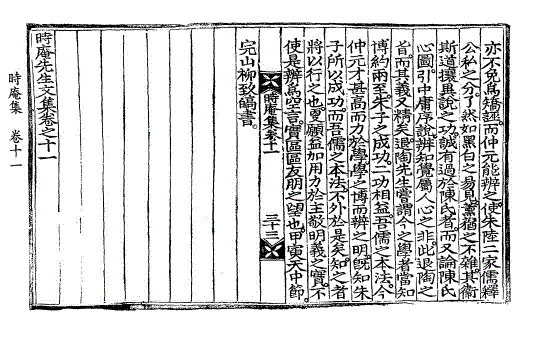 亦不免为矫诬。而仲元能辨之。使朱陆二家儒释公私之分。了然如黑白之易见。薰莸之不杂。其卫斯道攘异说之功。诚有过于陈氏者。而又论陈氏心图。引中庸序说。辨知觉属人心之非。此退陶之旨。而其义又精矣。退陶先生尝谓今之学者当知博约两至。朱子之成功。二功相益。吾儒之本法。今仲元才甚高而力于学。学之博而辨之明。既知朱子所以成功。而吾儒之本法。不外于是矣。知之者将以行之也。更愿益加用力于主敬明义之实。不使是辨为空言。实区区友朋之望也。甲寅天中节。完山柳致皓书。
亦不免为矫诬。而仲元能辨之。使朱陆二家儒释公私之分。了然如黑白之易见。薰莸之不杂。其卫斯道攘异说之功。诚有过于陈氏者。而又论陈氏心图。引中庸序说。辨知觉属人心之非。此退陶之旨。而其义又精矣。退陶先生尝谓今之学者当知博约两至。朱子之成功。二功相益。吾儒之本法。今仲元才甚高而力于学。学之博而辨之明。既知朱子所以成功。而吾儒之本法。不外于是矣。知之者将以行之也。更愿益加用力于主敬明义之实。不使是辨为空言。实区区友朋之望也。甲寅天中节。完山柳致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