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x 页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杂著
杂著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39H 页
 困勉录
困勉录至亲之服以期断。盖期年则天运一周。时物皆变。哀痛之情。思慕之心。至此亦变故也。惟父母为最亲而其恩为莫重。故又加一期。所谓加隆焉者是也。三年之丧。其实二期也。自期而下。以次降杀为大功为小功为缌麻。盖期年者四时也。九月者三时也。五月者两时也。三月者一时也。天道一时而少变。二时而又变。三时而又加变。四时而为一大变。哀情之浅深。随时而渐杀者。亦有迟速故也。两时合为六月。而小功之服不为六月者。盖服虽为死者设。而乃生者之所服也。故皆取阳数。三年之丧以月数则为二十五月。并禫而为二十七月。亦阳数也。自此以下皆然。此小功之所以不为六月也。其不为七月而必以五月者。盖七月则侵过三时之一月。而五月则才馀两时之一月也。期年服之重者。故引而伸之而为十三月。小功服之轻者。故进而减之而为五月也。
五服之轻重。缘情而隆杀。自己而推而上之。父母之丧三年。服祖以期。曾祖齐衰五月。高祖三月。推而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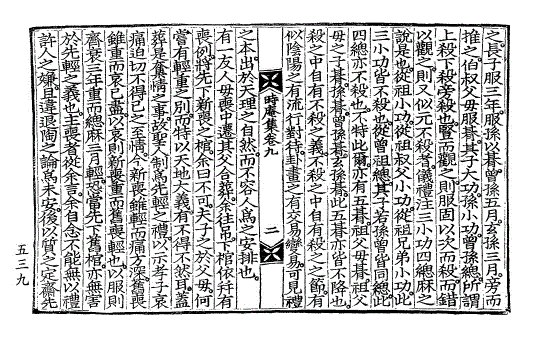 之。长子服三年。服孙以期。曾孙五月。玄孙三月。旁而推之。伯叔父母服期。其子大功。孙小功。曾孙缌。所谓上杀下杀旁杀也。竖而观之。则服固以次而杀。而错以观之。则又似元不杀者。仪礼注三小功四缌麻之说是也。从祖小功。从祖叔父小功。从祖兄弟小功。此三小功皆不杀也。从曾祖缌。其子若孙曾皆同缌。此四缌亦不杀也。不特此尔。亦有五期。祖父母期。祖父母之子期。孙期。曾孙期。玄孙期。此五期亦皆不降也。杀之中自有不杀之义。不杀之中自有杀之之节。有似阴阳之有流行对待。卦画之有交易变易。可见礼之本。出于天理之自然。而不容人为之安排也。
之。长子服三年。服孙以期。曾孙五月。玄孙三月。旁而推之。伯叔父母服期。其子大功。孙小功。曾孙缌。所谓上杀下杀旁杀也。竖而观之。则服固以次而杀。而错以观之。则又似元不杀者。仪礼注三小功四缌麻之说是也。从祖小功。从祖叔父小功。从祖兄弟小功。此三小功皆不杀也。从曾祖缌。其子若孙曾皆同缌。此四缌亦不杀也。不特此尔。亦有五期。祖父母期。祖父母之子期。孙期。曾孙期。玄孙期。此五期亦皆不降也。杀之中自有不杀之义。不杀之中自有杀之之节。有似阴阳之有流行对待。卦画之有交易变易。可见礼之本。出于天理之自然。而不容人为之安排也。有一友人母丧中迁其父合葬。余往吊。下棺依并有丧例。将先下新丧之棺。余曰不可。夫子之于父母。何尝有轻重之别。而特以天地大义。有不得不然耳。盖葬是夺情之事。故圣人制为先轻之礼。以示孝子哀痛迫切不得已之至情。今新丧虽轻而痛方深。旧丧虽重而哀已尽。以哀则新丧重而旧丧轻也。以服则齐衰三年重而缌麻三月轻。恐当先下旧棺。亦无害于先轻之义也。主丧者从余言。余自念不能无以礼许人之嫌。且违退陶之论为未安。后以质之定斋先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0H 页
 生。先生深然之曰。老先生守经之论。固后人之所当徵信。而盛论明白精密。求之人情而甚安。揆诸天理而不背。夫礼之生。原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苟合于天理人情。即礼之所行也。虽与老先生之训若相径廷。恐无害于两存也。先生之言如是。或庶几不至大谬否。(更详退陶说。乃为父丧中改葬母者言。与今日所处略有不同。妄论恐非有违于先生之训也。如何。)
生。先生深然之曰。老先生守经之论。固后人之所当徵信。而盛论明白精密。求之人情而甚安。揆诸天理而不背。夫礼之生。原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苟合于天理人情。即礼之所行也。虽与老先生之训若相径廷。恐无害于两存也。先生之言如是。或庶几不至大谬否。(更详退陶说。乃为父丧中改葬母者言。与今日所处略有不同。妄论恐非有违于先生之训也。如何。)今世士大夫遭子侄之丧。以为己下之服。而凡事简忽。略不加意。甚非也。朱子遭长子丧。既殡诸生具香烛之奠。先生留寒泉殡所受吊。望见客至。必涕泣远接之。客去必远送之。及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诸子不赴酒食会。近祥则举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颜色忧戚。盖如是而后。天理人情。庶可以两尽矣。
古者为师心丧三年。郑玄曰。心丧戚容。如丧父母而无服也。夫心丧云者。虽身无衰麻之服。而其哀痛之诚心。与丧君父无异也。哀痛在心则其居处服食。亦当自别于平常时也。圣人不制师生之服者。盖师生以义合者也。其恩义之轻重厚薄不齐。势不可立为一定之制也。程子所谓师不立服。不可立也。当以情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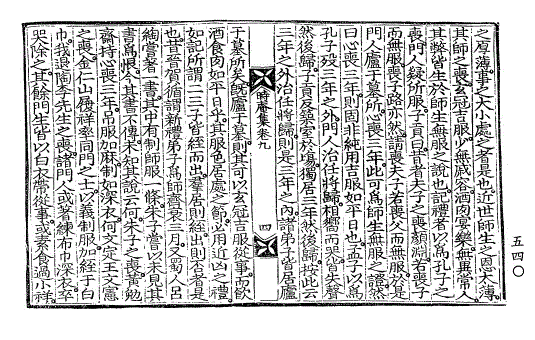 之厚薄。事之大小处之者是也。近世师生之恩太薄。其师之丧。玄冠吉服。少无戚容。酒肉宴乐。无异常人。其弊皆生于师生无服之说也。记礼者以为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门人庐于墓所。心丧三年。此可为师生无服之證。然曰心丧三年。则固非纯用吉服如平日也。孟子以为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按此云三年之外治任将归。则是三年之内。诸弟子皆居庐于墓所矣。既庐于墓。则其可以玄冠吉服从事。而饮酒食肉如平日乎。其服色居处之节。必用近凶之礼。如记所谓二三子皆绖而出。群居则绖。出则否者是也。昔晋贺循谓新礼弟子为师齐衰三月。又蜀人吕绹尝著一书。其中有制师服一条。朱子尝以未见其书为恨。今其书不传。未知其说云何。朱子之丧。黄勉斋持心丧三年。吊服加麻。制如深衣。何文定王文宪之丧。金仁山履祥率同门之士。以义制服。加绖于白巾。我退陶李先生之丧。诸门人或著练布巾深衣。卒哭除之。其馀门生皆以白衣带从事。或素食过小祥。
之厚薄。事之大小处之者是也。近世师生之恩太薄。其师之丧。玄冠吉服。少无戚容。酒肉宴乐。无异常人。其弊皆生于师生无服之说也。记礼者以为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门人庐于墓所。心丧三年。此可为师生无服之證。然曰心丧三年。则固非纯用吉服如平日也。孟子以为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按此云三年之外治任将归。则是三年之内。诸弟子皆居庐于墓所矣。既庐于墓。则其可以玄冠吉服从事。而饮酒食肉如平日乎。其服色居处之节。必用近凶之礼。如记所谓二三子皆绖而出。群居则绖。出则否者是也。昔晋贺循谓新礼弟子为师齐衰三月。又蜀人吕绹尝著一书。其中有制师服一条。朱子尝以未见其书为恨。今其书不传。未知其说云何。朱子之丧。黄勉斋持心丧三年。吊服加麻。制如深衣。何文定王文宪之丧。金仁山履祥率同门之士。以义制服。加绖于白巾。我退陶李先生之丧。诸门人或著练布巾深衣。卒哭除之。其馀门生皆以白衣带从事。或素食过小祥。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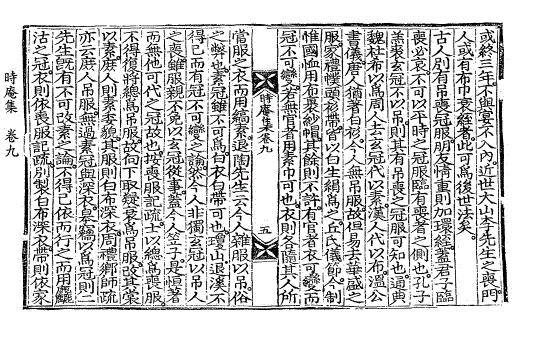 或终三年。不与宴不入内。近世大山李先生之丧。门人或有布巾衰绖者。此可为后世法矣。
或终三年。不与宴不入内。近世大山李先生之丧。门人或有布巾衰绖者。此可为后世法矣。古人别有吊丧冠服。朋友情重则加环绖。盖君子临丧必哀。不可以平时之冠服临有丧者之侧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吊。则其有吊丧之冠服可知也。通典魏杜希以为周人去玄冠代以素。汉人代以布。温公书仪。唐人犹著白衫。今人无吊服。故但易去华盛之服。家礼幞头衫带。皆以白生绢为之。丘氏仪节。今制惟国恤用布裹纱帽。其馀则不许。有官者衣可变而冠不可变。若无官者用素巾可也。衣则各随其人所当服之衣而用缟素。退陶先生云今人杂服以吊。俗之弊也。素冠虽不可为。白衣白带可也。琼山,退溪不得已而有冠不可变之论。然今人非独玄冠以吊人之丧。虽服亲不免以玄冠从事。盖今人笠子。是恒著而无他可代之冠故也。按丧服记疏。士以缌为丧服。不得复将缌为吊服。故向下取疑衰为吊服。改其裳以素。庶人则素委貌。其服则白布深衣。周礼乡师疏亦云庶人吊服。无过素冠与深衣。皋窃以为冠则二先生既有不可改素之论。不得已依而行之而用粗沽之冠。衣则依丧服记疏。别制白布深衣。带则依家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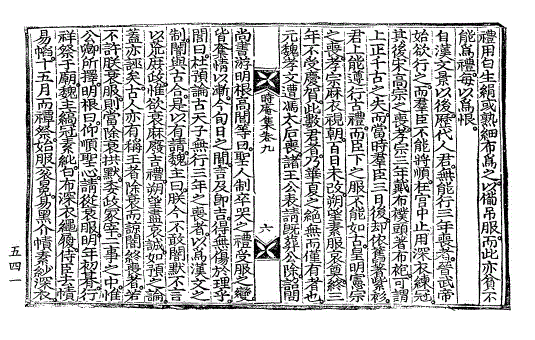 礼用白生绢或熟细布为之。以备吊服。而此亦贫不能为礼。每以为恨。
礼用白生绢或熟细布为之。以备吊服。而此亦贫不能为礼。每以为恨。自汉文景以后。历代人君。无能行三年丧者。晋武帝始欲行之。而群臣不能将顺。在宫中止用深衣练冠。其后宋高宗之丧。孝宗三年戴布襆头著布袍。可谓上正千古之失。而当时群臣三日后。却依旧著紫衫。君上能遵行古礼。而臣下之服不能如古。皇明宪宗之丧。孝宗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朔望素服哀奠。终三年不受庆贺。此数君者。乃华夏之绝无而仅有者也。元魏孝文遭冯太后丧。诸王公表请既葬公除。诏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曰。圣人制卒哭之礼受服之变。皆夺情以渐。今旬日之间。言及即吉。得无伤于理乎。闾曰。杜预论古天子无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闇与古合。是以有请。魏主曰。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如预之论。盖亦诬矣。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闇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择。明根曰。仰顺圣心。请从衰服。明年初期。行祥祭于庙。魏主缟冠素纰。白布深衣绳履。侍臣去帻易幍。十五月而禫祭。始服衮冕。易黑介帻素纱深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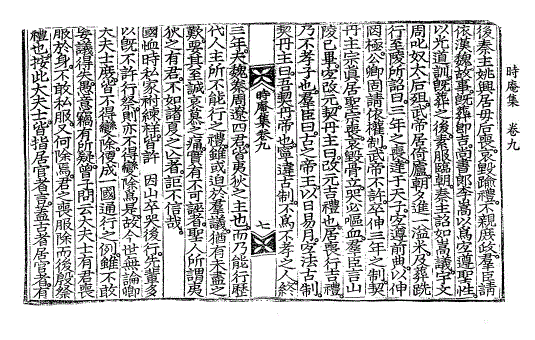 后秦主姚兴居母后丧。哀毁踰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以为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素服临朝。秦主诏如嵩议。宇文周叱奴太后殂。武帝居倚庐。朝夕进一溢米。及葬跣行至陵所诏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宜遵前典。以伸罔极。公卿固请依权制。武帝不许。卒伸三年之制。契丹主宗真居圣宗丧。哀毁骨立。哭必呕血。群臣言山陵已毕。宜改元。契丹主曰。改元吉礼也。居丧行吉礼。乃不孝子也。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契丹主曰。吾契丹帝也。宁违古制。不为不孝之人。终三年。夫魏秦周辽四君。皆夷狄之主也。而乃能行历代人主所不能行之礼。虽或迫于群议。犹有未尽之叹。要其至诚哀慕之痛。实有不可诬者。圣人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者。讵不信哉。
后秦主姚兴居母后丧。哀毁踰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以为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素服临朝。秦主诏如嵩议。宇文周叱奴太后殂。武帝居倚庐。朝夕进一溢米。及葬跣行至陵所诏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宜遵前典。以伸罔极。公卿固请依权制。武帝不许。卒伸三年之制。契丹主宗真居圣宗丧。哀毁骨立。哭必呕血。群臣言山陵已毕。宜改元。契丹主曰。改元吉礼也。居丧行吉礼。乃不孝子也。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契丹主曰。吾契丹帝也。宁违古制。不为不孝之人。终三年。夫魏秦周辽四君。皆夷狄之主也。而乃能行历代人主所不能行之礼。虽或迫于群议。犹有未尽之叹。要其至诚哀慕之痛。实有不可诬者。圣人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者。讵不信哉。国恤时私家祔练祥。皆许 因山卒哭后行。先辈多以既不许行祭。则亦不得变除为是。故今世无论卿大夫士庶。皆不得变除。便成一国通行之例。虽不敢妄议得失。愚意窃有所疑。曾子问云大夫士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按此大夫士。皆指居官者言。盖古者居官者。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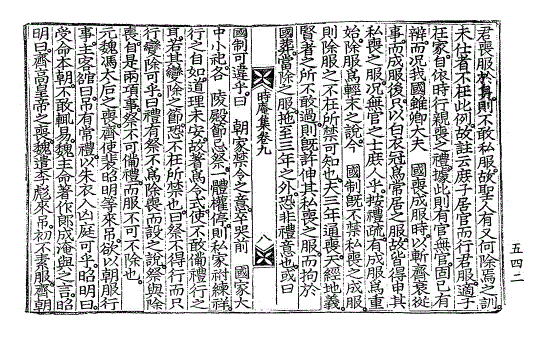 君丧服于身。则不敢私服。故圣人有又何除焉之训。未仕者不在此例。故注云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适子在家。自依时行亲丧之礼。据此则有官无官。固已有辨。而况我国虽卿大夫 国丧成服时。以斩齐衰从事。而成服后。只以白衣冠为常居之服。故皆得申其私丧之服。况无官之士庶人乎。按礼疏。有成服为重始。除服为轻末之说。今 国制既不禁私丧之成服。则除服之不在所禁可知也。夫三年通丧。天经地义。贤者之所不敢过。则既许伸其私丧之服。而拘于 国葬。当除之服。拖至三年之外。恐非礼意也。或曰 国制可违乎。曰 朝家禁令之意。卒哭前 国家大中小祀。各 陵殿节忌祭。一体权停。则私家祔练祥。行之自如。道理未安。故著为令式。使不敢备礼行之耳。若其变除之节。恐不在所禁也。曰祭不得行而只行变除可乎。曰礼有祭不为除丧而设之说。祭与除丧。自是两项事。祭不可备礼。而服不可不除也。
君丧服于身。则不敢私服。故圣人有又何除焉之训。未仕者不在此例。故注云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适子在家。自依时行亲丧之礼。据此则有官无官。固已有辨。而况我国虽卿大夫 国丧成服时。以斩齐衰从事。而成服后。只以白衣冠为常居之服。故皆得申其私丧之服。况无官之士庶人乎。按礼疏。有成服为重始。除服为轻末之说。今 国制既不禁私丧之成服。则除服之不在所禁可知也。夫三年通丧。天经地义。贤者之所不敢过。则既许伸其私丧之服。而拘于 国葬。当除之服。拖至三年之外。恐非礼意也。或曰 国制可违乎。曰 朝家禁令之意。卒哭前 国家大中小祀。各 陵殿节忌祭。一体权停。则私家祔练祥。行之自如。道理未安。故著为令式。使不敢备礼行之耳。若其变除之节。恐不在所禁也。曰祭不得行而只行变除可乎。曰礼有祭不为除丧而设之说。祭与除丧。自是两项事。祭不可备礼。而服不可不除也。元魏冯太后之丧。齐使裴昭明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官名)曰。吊有常礼。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曰。受命本朝。不敢辄易。魏主命著作郎成淹与之言。昭明曰。齐高皇帝之丧。魏遣李彪来吊。初不素服。齐朝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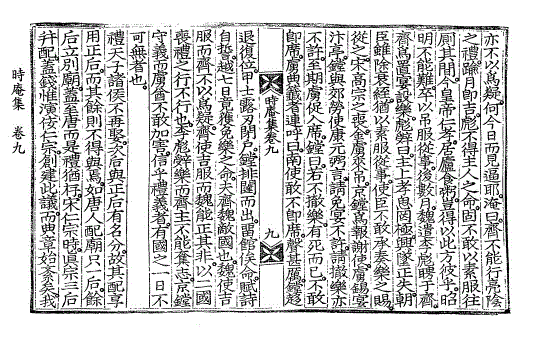 亦不以为疑。何今日而见逼耶。淹曰。齐不能行亮阴之礼。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厕其间。今皇帝仁孝。居庐食粥。岂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不能难。卒以吊服从事。后数月。魏遣李彪聘于齐。齐为置宴设乐。彪辞曰。主上孝思罔极。兴坠正失。朝臣虽除衰绖。犹以素服从事。使臣不敢承奏乐之赐。从之。宋高宗之丧。金虏来吊。京镗为报谢使。虏锡宴汴亭。镗与郊劳使康元弼言。请免宴不许。请撤樂亦不许。至期虏促入席。镗曰。若不撤乐。有死而已。不敢即席。虏典签者连呼曰。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厉。镗趍退复位。甲士露刃闭户。镗排闼而出。留馆俟命。赋诗自誓。越七日竟获免乐之命。夫齐魏敌国也。魏使吉服而齐不以为疑。齐使吉服而魏能正其非。以二国丧礼之行不行也。李彪辞乐而齐主不能夺志。京镗守义而虏酋不敢加害。信乎礼义者。有国之一日不可无者也。
亦不以为疑。何今日而见逼耶。淹曰。齐不能行亮阴之礼。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厕其间。今皇帝仁孝。居庐食粥。岂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不能难。卒以吊服从事。后数月。魏遣李彪聘于齐。齐为置宴设乐。彪辞曰。主上孝思罔极。兴坠正失。朝臣虽除衰绖。犹以素服从事。使臣不敢承奏乐之赐。从之。宋高宗之丧。金虏来吊。京镗为报谢使。虏锡宴汴亭。镗与郊劳使康元弼言。请免宴不许。请撤樂亦不许。至期虏促入席。镗曰。若不撤乐。有死而已。不敢即席。虏典签者连呼曰。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厉。镗趍退复位。甲士露刃闭户。镗排闼而出。留馆俟命。赋诗自誓。越七日竟获免乐之命。夫齐魏敌国也。魏使吉服而齐不以为疑。齐使吉服而魏能正其非。以二国丧礼之行不行也。李彪辞乐而齐主不能夺志。京镗守义而虏酋不敢加害。信乎礼义者。有国之一日不可无者也。礼天子诸侯不再娶。次后与正后有名分。故其配享用正后。而其馀则不得与焉。如唐人配庙只一后。馀后立别庙。盖至唐而是礼犹存。宋仁宗时。真宗三后并配。盖钱惟演佞仁宗。创建此议。而典章始紊矣。我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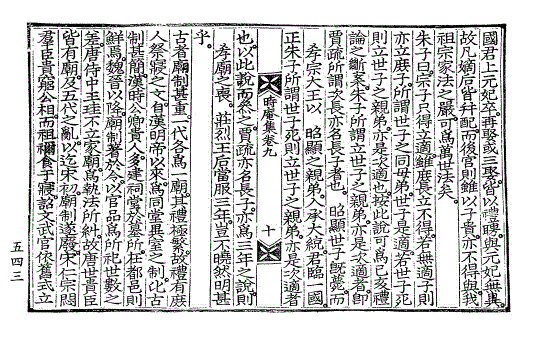 国君上元妃卒。再娶或三娶。皆以礼聘。与元妃无异。故凡嫡后皆并配。而后宫则虽以子贵。亦不得与。我祖宗家法之严。可为万世法矣。
国君上元妃卒。再娶或三娶。皆以礼聘。与元妃无异。故凡嫡后皆并配。而后宫则虽以子贵。亦不得与。我祖宗家法之严。可为万世法矣。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适。虽庶长立不得。若无适子则亦立庶子。所谓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适。若世子死则立世子之亲弟。亦是次适也。按此说可为己亥礼论之断案。朱子所谓立世子之亲弟。亦是次适者。即贾疏所谓次长亦名长子者也。 昭显世子既薨。而 孝宗大王以 昭显之亲弟。入承大统。君临一国。正朱子所谓世子死则立世子之亲弟。亦是次适者也。以此说而参之。贾疏亦名长子。亦为三年之说。则 孝庙之丧。 庄烈王后当服三年。岂不晓然明甚乎。
古者庙制甚重。一代各为一庙。其礼极繁。故礼有庶人祭寝之文。自汉明帝以来。为同堂异室之制。比古制甚简。汉时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魏晋以降。庙制著于令。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唐侍中王圭不立家庙。为执法所纠。故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之乱。以迄宋初。庙制遂废。宋仁宗闷群臣贵穷公相。而祖祢食于寝。诏文武官依旧式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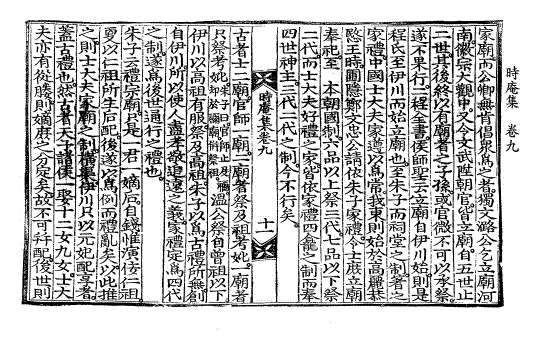 家庙。而公卿无肯倡众为之者。独文潞公乞立庙河南。徽宗大观中。又令文武升朝官。皆立庙。自五世止二世。其后终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遂不果行。二程全书。侯师圣云立庙自伊川始。则是程氏至伊川而始立庙也。至朱子而祠堂之制。著之家礼。中国士大夫家遵以为常。我东则始于高丽恭悯王时。圃隐郑文忠公请依朱子家礼。令士庶立庙奉祀。至 本朝国制。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祭二代。而士大夫好礼之家。皆依家礼四龛之制而奉四世神主。三代二代之制。今不行矣。
家庙。而公卿无肯倡众为之者。独文潞公乞立庙河南。徽宗大观中。又令文武升朝官。皆立庙。自五世止二世。其后终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遂不果行。二程全书。侯师圣云立庙自伊川始。则是程氏至伊川而始立庙也。至朱子而祠堂之制。著之家礼。中国士大夫家遵以为常。我东则始于高丽恭悯王时。圃隐郑文忠公请依朱子家礼。令士庶立庙奉祀。至 本朝国制。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祭二代。而士大夫好礼之家。皆依家礼四龛之制而奉四世神主。三代二代之制。今不行矣。古者士二庙。官师一庙。二庙者祭及祖考妣。一庙者只祭考妣。(朱子曰。官师止及祢。却于祢庙。并祭祖。)温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以高祖有服。祭及高祖。朱子以为古礼所无。创自伊川。所以使人尽孝敬追远之义。家礼定为四代之制。遂为后世通行之礼也。
朱子云礼宗庙。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钱惟演佞仁祖。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后遂以为例而礼乱矣。以此推之。则士大夫家庙之制。横渠,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者。盖古礼也。然古者天子诸侯一娶十二女九女。士大夫亦有从媵。则嫡庶之分定矣。故不可并配。后世则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4L 页
 虽再娶。皆以礼聘。皆正室也。故可以并配。故朱子以祭于别室为未安。
虽再娶。皆以礼聘。皆正室也。故可以并配。故朱子以祭于别室为未安。吾家自先世无前后配。先府君始再娶。余谓兄子孝源曰。考位忌日。并祭前后配。统于尊也。前配忌日。后配之出。后配忌日。前配之出。俱未妥当。源侄难之曰。考妣并祭。自是先祖之礼。则以前后配之故而止祭当位。似为未安。盖源侄以宗子主祀。有不可遽违其言而胶守浅见。就质于定斋先生。先生曰。以礼言之。盛论固然。而鄙家亦自先世并祭前后配。故今只得从之。盖此等事。苟无大害于义则从厚可也。皋窃伏念退陶先生尝曰忌祭共行。不应礼文。但某家自先世如此行之。故未敢改耳。定斋之论又如是。故竟依源侄之言。然至于吾身则事体又别。吾以先妣之命。三娶而始有子。吾死之后。只祭单位可也。子孙虽不再娶。皆当用此例。盖一庙之内。不可用二礼也。
古者四时正祭之外。又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之礼而已。唐宋以来。始有墓祭忌祭节祠之名。程子曰。随俗墓祭。不害义理。朱子曰。古无忌祭。近日诸先生方考及此。又曰既有正祭则存此(节祠)似亦无害。盖忌日者。丧之馀。丘墓是祖考体魄所藏。节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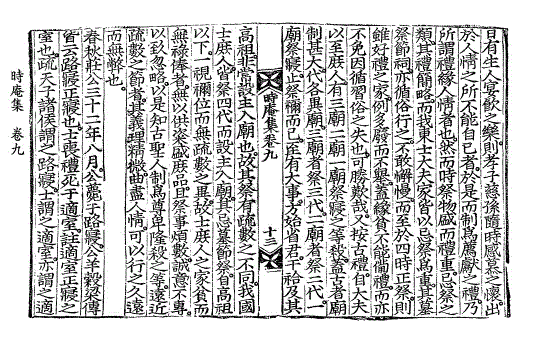 日有生人宴饮之乐。则孝子慈孙随时感慕之怀。出于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于是而制为荐献之礼。乃所谓礼缘人情者也。然而时祭物盛而礼重。忌祭之类。其礼简略。而我东士大夫家皆以忌祭为重。其墓祭节祠。亦循俗行之。不敢懈慢。而至于四时正祭。则虽好礼之家。例多废而不举。盖缘贫不能备礼。而亦不免因循习俗之失也。可胜叹哉。又按古礼。自大夫以至庶人。有三庙二庙一庙祭寝之等杀。盖古者庙制甚大。代各异庙。三庙者祭三代。二庙者祭二代。一庙祭寝。止祭祢而已。至有大事。方始省君。干祫及其高祖。非常设主入庙也。故其祭有疏数之不同。我国士庶人。皆祭四代而设主入庙。其忌墓节祭。自高祖以下。一视祢位而无疏数之异。故士庶人之家贫而无禄俸者。无以供粢盛庶品。且祭事烦数。诚意不专。以致忽略。以是知古圣人制为尊卑隆杀之等。远近疏数之节者。其义理精微。曲尽人情。可以行之久远而无弊也。
日有生人宴饮之乐。则孝子慈孙随时感慕之怀。出于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于是而制为荐献之礼。乃所谓礼缘人情者也。然而时祭物盛而礼重。忌祭之类。其礼简略。而我东士大夫家皆以忌祭为重。其墓祭节祠。亦循俗行之。不敢懈慢。而至于四时正祭。则虽好礼之家。例多废而不举。盖缘贫不能备礼。而亦不免因循习俗之失也。可胜叹哉。又按古礼。自大夫以至庶人。有三庙二庙一庙祭寝之等杀。盖古者庙制甚大。代各异庙。三庙者祭三代。二庙者祭二代。一庙祭寝。止祭祢而已。至有大事。方始省君。干祫及其高祖。非常设主入庙也。故其祭有疏数之不同。我国士庶人。皆祭四代而设主入庙。其忌墓节祭。自高祖以下。一视祢位而无疏数之异。故士庶人之家贫而无禄俸者。无以供粢盛庶品。且祭事烦数。诚意不专。以致忽略。以是知古圣人制为尊卑隆杀之等。远近疏数之节者。其义理精微。曲尽人情。可以行之久远而无弊也。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八月。公薨于路寝。公羊谷梁传皆云路寝正寝也。士丧礼死于适室。注适室正寝之室也。疏天子诸侯谓之路寝。士谓之适室。亦谓之适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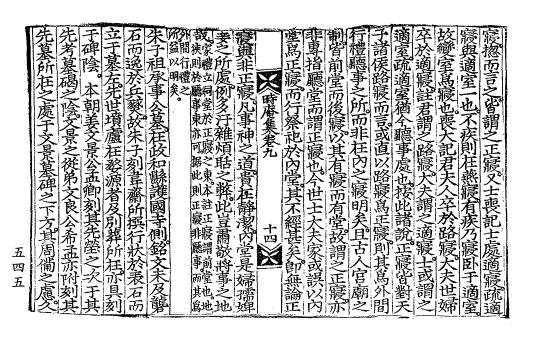 寝。揔而言之。皆谓之正寝。又士丧记。士处适寝。疏适寝与适室一也。不疾则在燕寝。有疾乃寝卧于适室。故变室为寝也。丧大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注君谓之路寝。大夫谓之适寝。士或谓之适室。疏适室犹今听事处也。按此诸说。正寝皆对天子诸侯路寝而言。或直以路寝为正寝。则其为外间行礼听事之所。而非在内之寝明矣。且古人宫庙之制。皆前堂而后寝。以其有寝而有堂。故谓之正寝。亦非专指厅堂而谓正寝也。今世士大夫家或误以内堂为正寝。而行祭祀于内堂。其不经甚矣。即无论正寝与非正寝。凡事神之道。贵在静洁。内堂是妇孺婢妾之所处。例多污杂烦聒之弊。此岂肃敬将事之地哉。(家礼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本注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东亦可。据此则正寝非厅事。而其为外间行礼之所。益以明矣。)
寝。揔而言之。皆谓之正寝。又士丧记。士处适寝。疏适寝与适室一也。不疾则在燕寝。有疾乃寝卧于适室。故变室为寝也。丧大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注君谓之路寝。大夫谓之适寝。士或谓之适室。疏适室犹今听事处也。按此诸说。正寝皆对天子诸侯路寝而言。或直以路寝为正寝。则其为外间行礼听事之所。而非在内之寝明矣。且古人宫庙之制。皆前堂而后寝。以其有寝而有堂。故谓之正寝。亦非专指厅堂而谓正寝也。今世士大夫家或误以内堂为正寝。而行祭祀于内堂。其不经甚矣。即无论正寝与非正寝。凡事神之道。贵在静洁。内堂是妇孺婢妾之所处。例多污杂烦聒之弊。此岂肃敬将事之地哉。(家礼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本注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东亦可。据此则正寝非厅事。而其为外间行礼之所。益以明矣。)朱子祖承事公墓。在政和县护国寺侧。铭文未及砻石而逸于兵燹。故朱子刻韦斋所撰行状于表石而立于墓左。先世坟庐在婺源者及别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阴。 本朝姜文景公孟卿刻其先茔之次于其先考墓碣之阴。文景之从弟文良公希孟亦附刻其先墓所在之处于文景墓碑之下方。其周备之虑。久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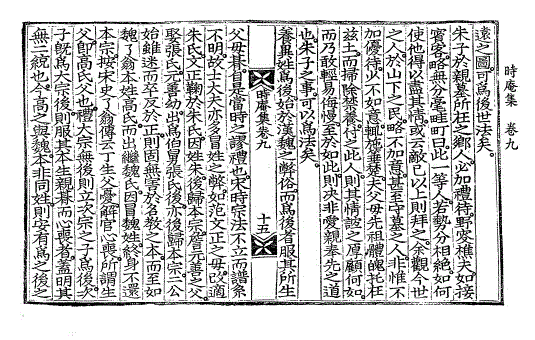 远之图。可为后世法矣。
远之图。可为后世法矣。朱子于亲墓所在之乡人。必加礼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畦町曰。此一等人。若势分相绝。如何使他得以尽其情。或云敌己以上则拜之。余观今世之人。于山下之民。略不加意。甚至守墓之人。非惟不加优待。少不如意。辄施箠楚。夫父母先祖体魄托在玆土。而扫除禁养。付之此人。则其情谊之厚顾何如。而乃敢轻易侮慢。至于如此。则决非爱亲奉先之道也。朱子之事。可以为法矣。
养异姓为后。始于汉魏之弊俗。而为后者服其所生父母期。自是当时之谬礼也。宋时宗法不立而谱系不明。故士大夫亦多冒姓之弊。如范文正之母。改适朱氏。文正鞠于朱氏。因姓朱。后归本宗。詹元善之父。娶张氏。元善幼。出为伯舅张氏后。亦后归本宗。二公始虽迷而卒反于正。则固无害于名教之本。而至如魏了翁本姓高氏。而出继魏氏。因冒魏姓。终身不还本宗。按宋史了翁传云丁生父忧。解官心丧。所谓生父。即高氏父也。礼大宗无后则立次宗之子为后。次子既为大宗后。则服其本生亲期而心丧者。盖明其无二统也。今高之与魏。本非同姓。则安有为之后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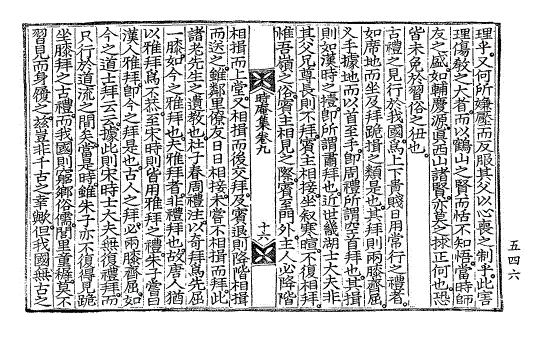 理乎。又何所嫌压而反服其父以心丧之制乎。此害理伤教之大者。而以鹤山之贤而恬不知悟。当时师友之盛。如辅庆源,真西山诸贤。亦莫之救正何也。恐皆未免于习俗之狃也。
理乎。又何所嫌压而反服其父以心丧之制乎。此害理伤教之大者。而以鹤山之贤而恬不知悟。当时师友之盛。如辅庆源,真西山诸贤。亦莫之救正何也。恐皆未免于习俗之狃也。古礼之见行于我国。为上下贵贱日用常行之礼者。如席地而坐及拜跪揖之类是也。其拜则两膝齐屈。叉手据地而以首至手。即周礼所谓空首拜也。其揖则如汉时之揖。即所谓肃拜也。近世畿湖士大夫非其父兄尊长则不拜。宾主相接。坐叙寒暄。不复相拜。惟吾岭之俗。宾主相见之际。宾至门外。主人必降阶相揖而上堂。又相揖而后交拜。及宾退则降阶相揖而送之。虽邻里僚友日日相接。未尝不相揖而拜。此诸老先生之遗教也。杜子春周礼注。以奇拜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也。夫雅拜者。非礼拜也。故唐人犹以雅拜为不恭。至宋时则皆用雅拜之礼。朱子尝曰汉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古人之拜。必两膝齐屈。如今之道士拜云云。据此则宋时士大夫无复礼拜。而只行于道流之间矣。当是时。虽朱子亦不复得见跪坐膝拜之古礼。而我国则穷乡俗儒。闾里童稚。莫不习见而身履之。玆岂非千古之幸欤。但我国无古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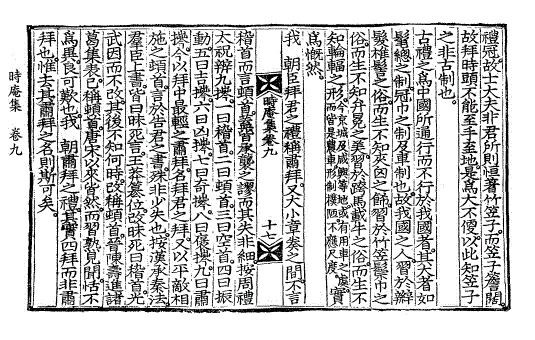 礼冠。故士大夫非君所则恒著竹笠子。而笠子檐阔。故拜时头不能至手至地。是为大不便。以此知笠子之非古制也。
礼冠。故士大夫非君所则恒著竹笠子。而笠子檐阔。故拜时头不能至手至地。是为大不便。以此知笠子之非古制也。古礼之为中国所通行而不行于我国者。其大者如髦总之制。冠巾之制及车制也。故我国之人。习于辫发椎髻之俗。而生不知夹囟之饰。习于竹笠鬃巾之俗。而生不知弁冕之美。习于跨马载牛之俗。而生不知轮辐之形。(今京城及咸兴等地。或有用车之处。而皆是农车。形制朴陋。不应尺度。)实为慨然。
我 朝臣拜君之礼称肃拜。又大小章奏之间。不言稽首而言顿首。盖皆承袭之谬而其失非细。按周礼太祝辨九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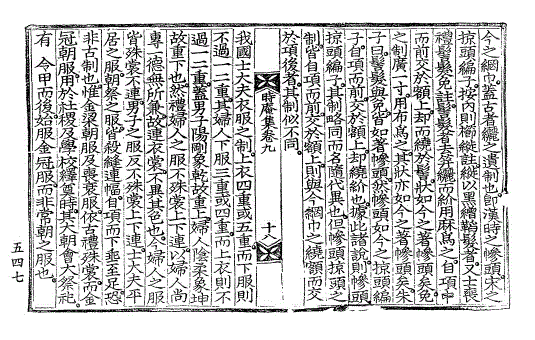 今之网巾。盖古者纚之遗制也。即汉时之幓头。宋之掠头编子。按内则栉縰注。縰以黑缯韬发者。又士丧礼髻发免注。髻发者去笄纚而紒用麻为之。自项中而前交于额上。却而绕于髻。状如今之著幓头矣。免之制广一寸。用布为之。其状亦如今之著幓头矣。朱子曰。髻发与免。皆如著幓头。然幓头如今之掠头编子。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却绕紒也。据此诸说。则幓头,掠头编子。其制略同而名随代异也。但幓头掠头之制。皆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则与今网巾之绕额而交于项后者。其制似不同。
今之网巾。盖古者纚之遗制也。即汉时之幓头。宋之掠头编子。按内则栉縰注。縰以黑缯韬发者。又士丧礼髻发免注。髻发者去笄纚而紒用麻为之。自项中而前交于额上。却而绕于髻。状如今之著幓头矣。免之制广一寸。用布为之。其状亦如今之著幓头矣。朱子曰。髻发与免。皆如著幓头。然幓头如今之掠头编子。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却绕紒也。据此诸说。则幓头,掠头编子。其制略同而名随代异也。但幓头掠头之制。皆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则与今网巾之绕额而交于项后者。其制似不同。我国士大夫衣服之制。上衣四重或五重。而下服则不过一二重。其妇人下服三重或四重。而上衣则不过一二重。盖男子阳刚象乾故重上。妇人阴柔象坤故重下也。然礼妇人之服不殊裳上下连。以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故连衣裳。不异其色也。今妇人之服皆殊裳不连。男子之服反不殊裳上下连。士大夫平居之服。朝祭之服。皆杀缝连幅。自项而下垂至足。恐非古制也。惟金梁朝服及丧衰服。依古礼殊裳。而金冠朝服。用于社稷及学校释奠时。其大朝会大祭祀。有 令甲而后。始服金冠服。而非常朝之服也。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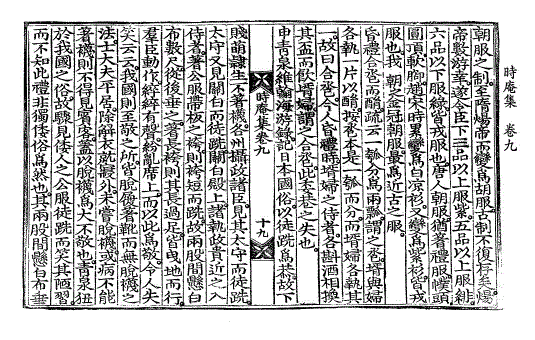 朝服之制。至隋炀帝而变为胡服。古制不复存矣。炀帝数游幸。遂令臣下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以下服绿。皆戎服也。唐人朝服。犹著礼服。幞头,圆顶,软脚。赵宋时累变为白凉衫。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我 朝之金冠朝服。最为近古之服。
朝服之制。至隋炀帝而变为胡服。古制不复存矣。炀帝数游幸。遂令臣下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以下服绿。皆戎服也。唐人朝服。犹著礼服。幞头,圆顶,软脚。赵宋时累变为白凉衫。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我 朝之金冠朝服。最为近古之服。昏礼合卺而酳。疏云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卺。婿与妇各执一片以酳。按卺本是一瓠而分。而婿妇各执其一。故曰合卺。今人昏礼时。婿妇之侍者。各斟酒相换其杯而饮婿妇。谓之合卺。此委巷之失也。
申青泉维翰海游录。记日本国俗。以徒跣为恭。故下贱萌隶生不著袜。各州摄政诸臣。见其太守而徒跣。太守又见关白而徒跣。关白殿上。诸执政贵近之入侍者。著公服带板之裤。则裤短而跣。故两股间悬白布数尺。从后垂之。著长裤则其长过足。皆曳地而行。群臣动作。綷綷有声。纷乱席上。而以此为敬。令人失笑云云。我国则至敬之所。皆脱履著靴而无脱袜之法。士大夫平居。除解衣就寝外。未尝脱袜。或病不能著袜则不得见宾客。盖以脱袜为大不敬也。青泉狃于我国之俗。故骤见倭人之公服徒跣而笑其陋习。而不知此礼非独倭俗为然也。其两股间悬白布垂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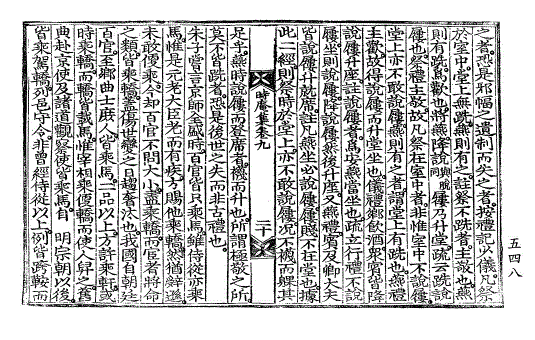 之者。恐是邪幅之遗制而失之者。按礼记少仪。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则有跣。为欢也。将燕。降说(与脱同)屦乃升堂。疏云跣说屦也。祭礼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说屦。堂上亦不敢说屦。燕则有之者。谓堂上有跣也。燕礼主欢。故得说屦而升堂坐也。仪礼乡饮酒。众宾皆降说屦升座。注说屦者。为安燕当坐也。疏立行礼不说屦。坐则说屦。降说屦然后升座。又燕礼。宾及卿大夫皆说屦升就席。注凡燕坐必说屦。屦贱不在堂也。据此二经。则祭时于堂上。亦不敢说屦。况不袜而裸其足乎。燕时说屦而登席者。袜而升也。所谓极敬之所。莫不皆跣者。恐是后世之失而非古礼也。
之者。恐是邪幅之遗制而失之者。按礼记少仪。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则有跣。为欢也。将燕。降说(与脱同)屦乃升堂。疏云跣说屦也。祭礼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说屦。堂上亦不敢说屦。燕则有之者。谓堂上有跣也。燕礼主欢。故得说屦而升堂坐也。仪礼乡饮酒。众宾皆降说屦升座。注说屦者。为安燕当坐也。疏立行礼不说屦。坐则说屦。降说屦然后升座。又燕礼。宾及卿大夫皆说屦升就席。注凡燕坐必说屦。屦贱不在堂也。据此二经。则祭时于堂上。亦不敢说屦。况不袜而裸其足乎。燕时说屦而登席者。袜而升也。所谓极敬之所。莫不皆跣者。恐是后世之失而非古礼也。朱子尝言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方赐他乘轿。然犹辞逊。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盖伤世变之日趋奢汰也。我国自朝廷百官。至乡曲士庶人。皆乘马。二品以上。方许乘轩。或时乘轿。而轿皆载马。惟宰相乘便轿而使人舁之。旧典赴京使及诸道观察使皆乘马。自 明宗朝以后。皆乘驾轿。列邑守令。非曾经侍从以上。例皆跨鞍而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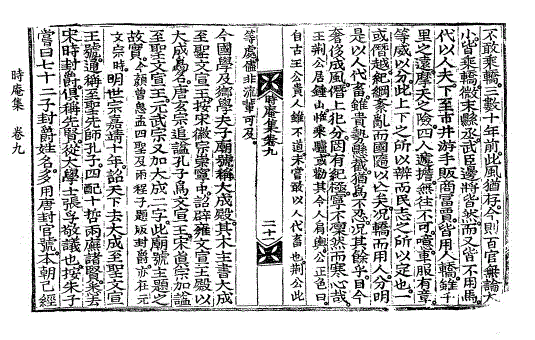 不敢乘轿。三数十年前。此风犹存。今则百官无论大小。皆乘轿。微末县丞。武臣边将皆然。而又皆不用马。代以人夫。下至市井游手贩商富贾。皆用人轿。虽千里之远。摩天之险。四人递担。无往不可。噫。车服有章。等威以分。此上下之所以辨而民志之所以定也。一或僭越。纪纲紊乱而国随以亡矣。况轿而用人。分明是以人代畜。虽贵势悬截。犹为不忍。况其馀乎。目今奢侈成风。僭上犯分。罔有纪极。宁不凛然而寒心哉。(王荆公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贵人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荆公此等处。尽非流辈可及。)
不敢乘轿。三数十年前。此风犹存。今则百官无论大小。皆乘轿。微末县丞。武臣边将皆然。而又皆不用马。代以人夫。下至市井游手贩商富贾。皆用人轿。虽千里之远。摩天之险。四人递担。无往不可。噫。车服有章。等威以分。此上下之所以辨而民志之所以定也。一或僭越。纪纲紊乱而国随以亡矣。况轿而用人。分明是以人代畜。虽贵势悬截。犹为不忍。况其馀乎。目今奢侈成风。僭上犯分。罔有纪极。宁不凛然而寒心哉。(王荆公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贵人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荆公此等处。尽非流辈可及。)今国学及乡学夫子庙号称大成殿。其木主书大成至圣文宣王。按宋徽宗崇宁中。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谥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又加大成二字。此庙号主题之故实。(今颜曾思孟四圣及两程子题版封爵。亦在元文宗时。)明世宗嘉靖十年。诏天下去大成至圣文宣王号。通称至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诸贤。悉去宋时封爵。俱称先贤。从太学士张孚敬议也。按朱子尝曰七十二子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号。本朝已经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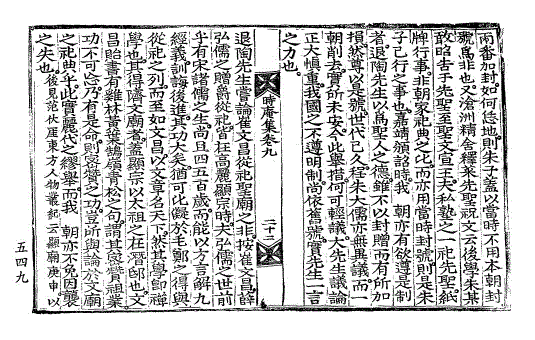 两番加封。如何恁地。则朱子盖以当时不用本朝封号为非也。又沧洲精舍释菜先圣祝文云后学朱某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夫私塾之一祀先圣。纸牌行事。非朝家祀典之比。而亦用当时封号。则是朱子已行之事也。嘉靖颁诏时。我 朝亦有欲遵是制者。退陶先生以为圣人之德。虽不以封赠而有所加损。然尊以是号。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无异议。而一朝削去。实所未安。今此举措。何可轻议。大先生议论正大慎重。我国之不遵明制。尚依旧号。实先生一言之力也。
两番加封。如何恁地。则朱子盖以当时不用本朝封号为非也。又沧洲精舍释菜先圣祝文云后学朱某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夫私塾之一祀先圣。纸牌行事。非朝家祀典之比。而亦用当时封号。则是朱子已行之事也。嘉靖颁诏时。我 朝亦有欲遵是制者。退陶先生以为圣人之德。虽不以封赠而有所加损。然尊以是号。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无异议。而一朝削去。实所未安。今此举措。何可轻议。大先生议论正大慎重。我国之不遵明制。尚依旧号。实先生一言之力也。退陶先生尝论崔文昌从祀圣庙之非。按崔文昌,薛弘儒之赠爵从祀。皆在高丽显宗时。夫弘儒之世前乎有宋诸儒之生。尚且四五百岁。而能以方言解九经义。训诲后进。其功大矣。犹可比儗于毛郑之得与从祀之列。而至如文昌。以文章名天下。然其学即禅学也。其得隮文庙者。盖显宗以太祖之在潜邸也。文昌贻书有鸡林黄叶鹄岭青松之句。谓其密赞祖业。功不可忘。乃有是命。则密赞之功。岂所与论于文庙之祀典乎。此实丽代之缪举。而我 朝亦不免因袭之失也。(后见范伏厓东方人物丛纪云显庙庚申。以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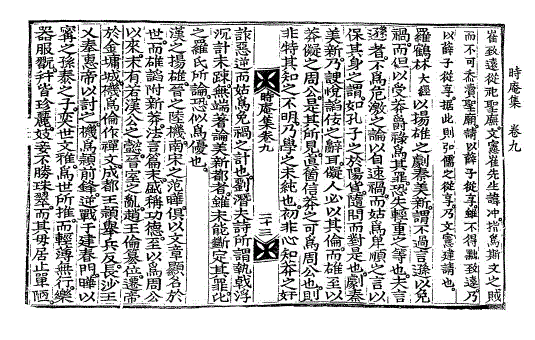 崔致远从祀圣庑。文宪崔先生讳冲。指为斯文之贼而不可忝渎圣庙。请以薛子从享。虽不得黜致远。乃以薛子从享。据此则弘儒之从享。乃文宪建请也。)
崔致远从祀圣庑。文宪崔先生讳冲。指为斯文之贼而不可忝渎圣庙。请以薛子从享。虽不得黜致远。乃以薛子从享。据此则弘儒之从享。乃文宪建请也。)罗鹤林(大经)以扬雄之剧秦美新。谓不过言逊以免祸。而但以受莽爵禄为其罪。恐失轻重之等也。夫言逊者。不为危激之论以自速祸。而姑为卑顺之言以保其身之谓。如孔子之于阳货。随问而对是也。剧秦美新。乃谀悦谄佞之辞耳。儗人必以其伦。而雄至以莽儗之周公。是其所见。真个信莽之可为周公也。则非特其知之不明。乃学之未纯也。初非心知莽之奸诈恶逆而姑为免祸之计也。刘潜夫诗所谓执戟浮沉计未疏。无端著论美新都者。虽未能断定其罪。比之罗氏所论。恐似为优也。
汉之扬雄。晋之陆机。南宋之范晔。俱以文章显名于世。而雄谄附新莽。法言篇末。盛称功德。至以为周公以来。未有若汉公之懿。晋室之乱。赵王伦篡位。迁帝于金墉城。机为伦作禅文。成都王颖举兵反。长沙王乂奉惠帝以讨之。机为颖前锋。逆战于建春门。晔以宁之孙泰之子。奕世文雅。为世所推。而轻薄无行。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不胜珠翠。而其母居止单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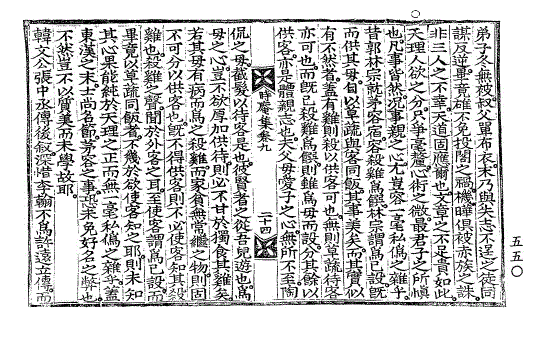 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末乃与失志不逞之徒同谋反逆。毕竟雄不免投阁之祸。机,晔俱被赤族之诛。非三人之不幸。天道固应尔也。文章之不足贵如此。
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末乃与失志不逞之徒同谋反逆。毕竟雄不免投阁之祸。机,晔俱被赤族之诛。非三人之不幸。天道固应尔也。文章之不足贵如此。天理人欲之分。只争毫釐。心术之微。最君子之所慎也。凡事皆然。况事亲之心。尤岂容一毫私伪之杂乎。昔郭林宗就茅容宿。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其事美矣。而其实似有不然者。盖有鸡则杀以供客可也。无则草蔬待客亦可也。而既已杀鸡为馔。则虽为母而设。分其馀以供客。亦是体亲志也。夫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陶侃之母。截发以待客是也。彼贤者之从吾儿游也。为母之心。岂不欲厚加供待。则必不甘于独食其鸡矣。若其母有病而为之杀鸡。而家贫无常继之物。则固不可分以供客也。既不得供客则不必使客知其杀鸡也。杀鸡之声。闻于外客之耳。至使客谓为己设。而毕竟以草蔬同饭者。不几于欲使客知之耶。则未知其心果能纯于天理之正而无一毫私伪之杂乎。盖东汉之末。士尚名节。茅容之事。恐未免好名之弊也。不然岂不以质美而未学故耶。
韩文公张中丞传后叙。深惜李翰不为许远立传。而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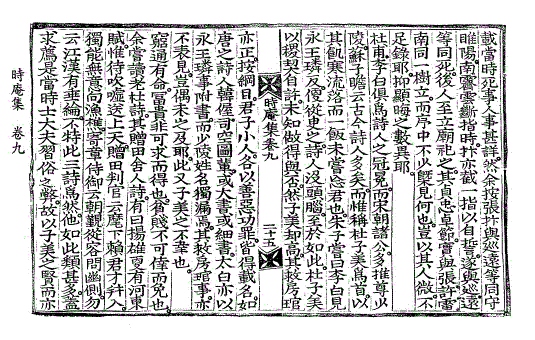 载当时死事人事甚详。然余按张抃与巡远等同守睢阳。南霁云断指时。抃亦截一指以自誓。遂与巡,远等同死。后人至立庙祀之。其贞忠卓节。实与张,许,雷,南同一树立。而序中不少槩见何也。岂以其人微。不足录耶。抑显晦之数异耶。
载当时死事人事甚详。然余按张抃与巡远等同守睢阳。南霁云断指时。抃亦截一指以自誓。遂与巡,远等同死。后人至立庙祀之。其贞忠卓节。实与张,许,雷,南同一树立。而序中不少槩见何也。岂以其人微。不足录耶。抑显晦之数异耶。杜甫,李白俱为诗人之冠冕。而宋朝诸公。多推尊少陵。苏子瞻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称杜子美为首。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朱子尝曰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按纲目。君子小人。各以善恶功罪。皆得载名。如唐之诗人韩偓,司空图辈。或大书或细书。太白亦以永王璘事附书。而少陵姓名独漏焉。其救房琯事。亦不表见。岂偶未之及耶。此又子美之不幸也。
穷通有命。富贵非可求而得也。贫贱不可倖而免也。余尝读老杜诗。其赠田舍人诗。有曰扬雄更有河东赋。惟待吹嘘送上天。赠田判官云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寄章侍御云朝觐从容问幽侧。勿云江汉有垂纶。不特此三诗为然。他如此类甚多。盖求荐是当时士大夫习俗之弊。故以子美之贤而亦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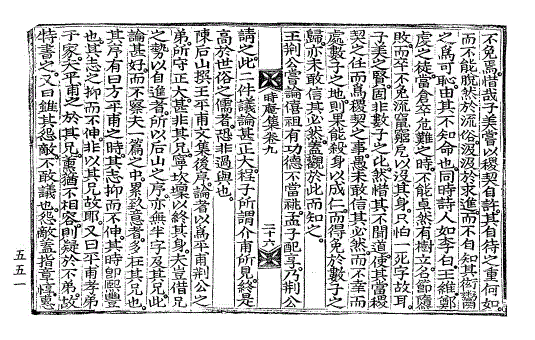 不免焉。惜哉子美尝以稷契自许。其自待之重何如。而不能脱然于流俗。汲汲于求进。而不自知其衒鬻之为可耻。由其不知命也。同时诗人如李白,王维,郑虔之徒。当仓卒危难之时。不能卓然有树立。名节隳败。而卒不免流窜穷厄以没其身。只怕一死字故耳。子美之贤。固非数子之比。然惜其不闻道。使其当稷契之任而为稷契之事。愚未敢信其必然。而不幸而处数子之地。则果能杀身以成仁。而得免于数子之归。亦未敢信其必然。盖观于此而知之。
不免焉。惜哉子美尝以稷契自许。其自待之重何如。而不能脱然于流俗。汲汲于求进。而不自知其衒鬻之为可耻。由其不知命也。同时诗人如李白,王维,郑虔之徒。当仓卒危难之时。不能卓然有树立。名节隳败。而卒不免流窜穷厄以没其身。只怕一死字故耳。子美之贤。固非数子之比。然惜其不闻道。使其当稷契之任而为稷契之事。愚未敢信其必然。而不幸而处数子之地。则果能杀身以成仁。而得免于数子之归。亦未敢信其必然。盖观于此而知之。王荆公尝论僖祖有功德不当祧。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此二件议论甚正大。程子所谓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者。恐非过与也。
陈后山撰王平甫文集后序。论者以为平甫荆公之弟。所守正大。甚非其兄。宁坎壈以终其身。夫岂借兄之势以自进者。所以后山之序。亦无半字及其兄。此论甚好。而不察夫一篇之中。累致意者。多在其兄也。其序有曰方平甫之时。其志抑而不伸。其时即熙丰也。其志之抑而不伸。非以其兄故耶。又曰平甫孝弟于家。夫平甫之于其兄。薰莸不相容。则疑于不弟。故特书之。又曰虽其怨敌。不敢议也。怨敌盖指章惇,惠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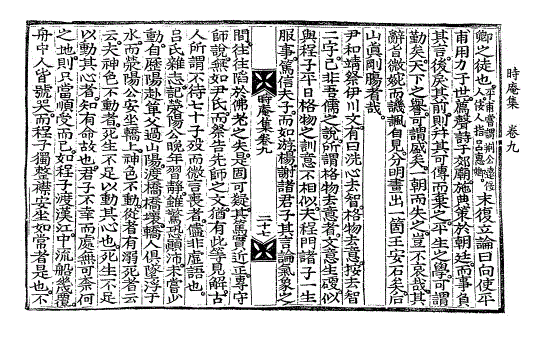 卿之徒也。(平甫尝谓荆公远佞人。佞人指吕惠卿。)末复立论曰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荐声诗于郊庙。施典策于朝廷。而事负其言。后戾其前。则并其可传而弃之。平生之学。可谓勤矣。天下之誉。可谓盛矣。一朝而失之。岂不哀哉。其辞旨微婉而讥讽自见。分明画出一个王安石矣。后山真刚肠者哉。
卿之徒也。(平甫尝谓荆公远佞人。佞人指吕惠卿。)末复立论曰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荐声诗于郊庙。施典策于朝廷。而事负其言。后戾其前。则并其可传而弃之。平生之学。可谓勤矣。天下之誉。可谓盛矣。一朝而失之。岂不哀哉。其辞旨微婉而讥讽自见。分明画出一个王安石矣。后山真刚肠者哉。尹和靖祭伊川文。有曰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按去智二字。已非吾儒之说。所谓格物去意者。文意生硬。似与程子平日格物之训意不相似。夫程门诸子一生服事。笃信夫子。而如游,杨,谢诸君子其言论气象之间。往往陷于佛老之失。是固可疑。其笃实近正。专守师说。无如尹氏。而祭告先师之文。犹有此等见解。古人所谓不待七十子殁而微言丧者。尽非虚语也。
吕氏杂志。记荥阳公晚年习静。虽惊恐颠沛。未尝少动。自历阳赴单父过山阳。渡桥桥坏。轿人俱坠浮于水。而荥阳公安坐轿上。神色不动。从者有溺死者云云。夫神色不动者。死生不足以动其心也。死生不足以动其心者。知有命故也。君子不幸而处无可柰何之地。则只当顺受而已。如程子渡汉江。中流船几覆。舟中人皆号哭。而程子独整襟安坐如常者是也。不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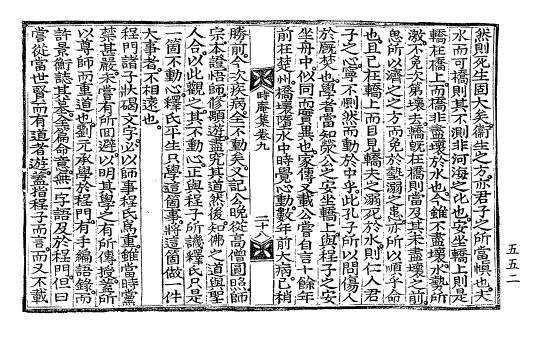 然则死生固大矣。卫生之方。亦君子之所当慎也。夫水而可桥则其不测非河海之比也。安坐轿上则是轿在桥上。而桥非尽坏于水也。今虽不尽坏。水势所激。不免次第坏去。轿既在桥则当及其未尽坏之前。思所以济之之方而免于垫溺之患。亦所以顺乎命也。且己在轿上而目见轿夫之溺死于水。则仁人君子之心。宁不恻然而动于中乎。此孔子所以问伤人于厩焚也。学者当知荥公之安坐轿上。与程子之安坐舟中。似同而实异也。家传又载公尝自言十馀年前在楚州。桥坏堕水中时觉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稍胜前。今次疾病。全不动矣。又记公晚从高僧圆照,师宗,本證,悟师,修颙游。尽究其道然后。知佛之道与圣人合。以此观之。其不动心。正与程子所讥释氏只是一个不动心。释氏平生只学这个事。将这个做一件大事者。不相远也。
然则死生固大矣。卫生之方。亦君子之所当慎也。夫水而可桥则其不测非河海之比也。安坐轿上则是轿在桥上。而桥非尽坏于水也。今虽不尽坏。水势所激。不免次第坏去。轿既在桥则当及其未尽坏之前。思所以济之之方而免于垫溺之患。亦所以顺乎命也。且己在轿上而目见轿夫之溺死于水。则仁人君子之心。宁不恻然而动于中乎。此孔子所以问伤人于厩焚也。学者当知荥公之安坐轿上。与程子之安坐舟中。似同而实异也。家传又载公尝自言十馀年前在楚州。桥坏堕水中时觉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稍胜前。今次疾病。全不动矣。又记公晚从高僧圆照,师宗,本證,悟师,修颙游。尽究其道然后。知佛之道与圣人合。以此观之。其不动心。正与程子所讥释氏只是一个不动心。释氏平生只学这个事。将这个做一件大事者。不相远也。程门诸子状碣文字。必以师事程氏为重。虽当时党禁甚严。未尝有所回避。以明其学之有所传授。盖所以尊师而重道也。刘元承学于程门。有手编语录。而许景衡志其墓。全篇命意。无一字语及于程门。但曰尝从当世贤而有道者游。盖指程子而言。而又不载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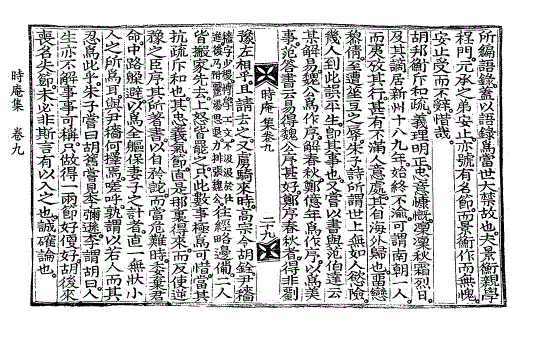 所编语录。盖以语录为当世大禁故也。夫景衡亲学程门。元承之弟安止。亦号有名节。而景衡作而无愧。安止受而不辞。惜哉。
所编语录。盖以语录为当世大禁故也。夫景衡亲学程门。元承之弟安止。亦号有名节。而景衡作而无愧。安止受而不辞。惜哉。胡邦衡斥和疏。义理明正。忠意慷慨。凛凛秋霜烈日。及其谪居新州十八九年。始终不渝。可谓南朝一人。而夷考其行。甚有不满人意处。其自海外归也。留恋黎倩。至遭莝豆之辱。朱子诗所谓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即其事也。又尝以书与范伯达云某解易。魏公为作序。解春秋。郑亿年为作序。以为美事。范答书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郑序春秋者。得非刘豫左相乎。且请去之。又虏骑来时。高宗令胡铨,尹穑(穑字少稷。博学工文。不汲汲于仕进。后乃附丽汤思退。力排张魏公。)往经略边备。二人皆搬家先去。上怒皆罢之。只此数事极为可惜。当其抗疏斥和也。其忠义气节。直是那里得来。而反使逆豫之臣序其所著书。以自矜詑。而当危难时。委弃君命。中路躲避。以为全躯保妻子之计者。直一无状小人之所为耳。与尹穑何择焉。嗟呼。孰谓以若人而其忍为此乎。朱子尝曰胡旧尝见李弥逊。李谓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称。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胡后来丧名失节。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诚确论也。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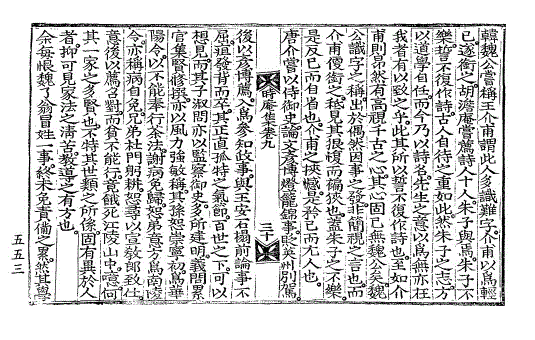 韩魏公尝称王介甫谓此人多识难字。介甫以为轻己。遂衔之。胡澹庵尝荐诗人十人。朱子与焉。朱子不乐。誓不复作诗。古人自待之重如此。然朱子之志。方以道学自任。而今乃以诗名。先生之意以为无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乎。此其所以誓不复作诗也。至如介甫则昂然有高视千古之心。其心固已无魏公矣。魏公识字之称。出于偶然因事之发。非简视之言也。而介甫便衔之。秪见其狠愎而褊狭也。盖朱子之不乐。是反己而自省也。介甫之挟憾。是矜己而尤人也。
韩魏公尝称王介甫谓此人多识难字。介甫以为轻己。遂衔之。胡澹庵尝荐诗人十人。朱子与焉。朱子不乐。誓不复作诗。古人自待之重如此。然朱子之志。方以道学自任。而今乃以诗名。先生之意以为无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乎。此其所以誓不复作诗也。至如介甫则昂然有高视千古之心。其心固已无魏公矣。魏公识字之称。出于偶然因事之发。非简视之言也。而介甫便衔之。秪见其狠愎而褊狭也。盖朱子之不乐。是反己而自省也。介甫之挟憾。是矜己而尤人也。唐介尝以侍御史。论文彦博灯笼锦事。贬英州别驾。后以彦博荐。入为参知政事。与王安石榻前论事不屈。疽发背而卒。其正直孤特之气节。百世之下。可以想见。而其子淑问亦以监察御史。多所建明。义问累官集贤修撰。亦以风力强敏称。其孙恕崇宁初。为华阳令。以不能奉行茶法。谢病免归。恕弟意方为南陵令。亦称病自免。兄弟杜门躬耕。恕寻以宣教郎致仕。意后以荐召对。而贫不能行。竟饿死江陵山中。噫。何其一家之多贤也。不特其世类之所系。固有异于人者。抑可见家法之清苦。教导之有方也。
余每恨魏了翁冒姓一事。终未免责备之累。然其学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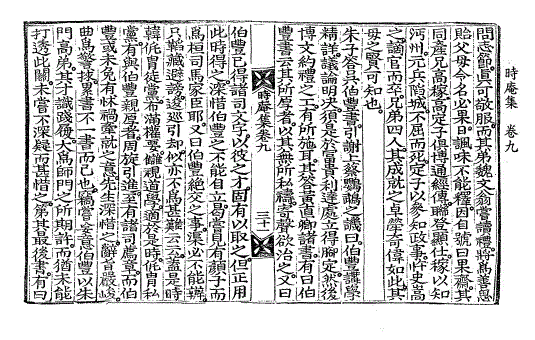 问志节。真可敬服。而其弟魏文翁尝读礼。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日讽味不能释。因自号曰果斋。其同产兄高稼,高定子俱博通经传。联登显仕。稼以知沔州。元兵陷城。不屈而死。定子以参知政事。忤史嵩之。谪官而卒。兄弟四人。其成就之卓荦奇伟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也。
问志节。真可敬服。而其弟魏文翁尝读礼。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日讽味不能释。因自号曰果斋。其同产兄高稼,高定子俱博通经传。联登显仕。稼以知沔州。元兵陷城。不屈而死。定子以参知政事。忤史嵩之。谪官而卒。兄弟四人。其成就之卓荦奇伟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也。朱子答吴伯丰书。引谢上蔡鹦鹉之讥曰。伯丰讲学精详。议论明决。须是于富贵利达处立得脚定。然后博文约礼之工。有所施耳。其答黄直卿诸书。有曰伯丰书云其所厚者。以其无所私祷。寄声欲治之。又曰伯丰已得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时得之。深惜伯丰之不能自立。曷尝见有颜子而为桓司马家臣耶。又曰伯丰绝交之事。渠必不能办。只韬藏避谤。逡巡引却。似亦不为甚难云云。盖是时韩侂胄徒党。布满权要。雠视道学。适于是时。侂胄私党。有与伯丰亲厚者。周旋引进。至有诸司荐章。而伯丰或未免有怵祸牵就之意。先生深惜之。辞旨严峻。曲为警救。累书不一书而已也。窃尝妄意伯丰以朱门高弟。其才识践履。大为师门之所期许。而犹未能打透此关。未尝不深疑而甚惜之。第其最后书。有曰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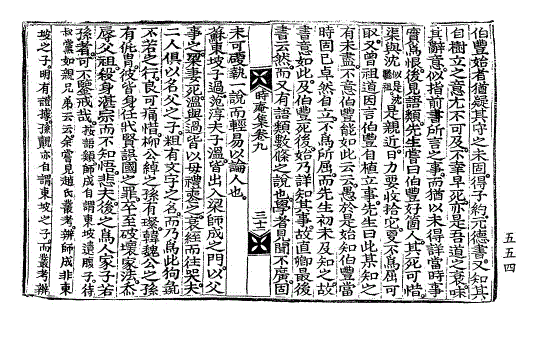 伯丰始者犹疑其守之未固。得子约,元德书。又知其自树立之意尤不可及。不幸早死。亦是吾道之衰。味其辞意。似指前书所言之事。而犹以未得详当时事实为恨。后见语类。先生尝曰伯丰好个人。其死可惜。渠与沈(似是沈继祖)是亲近。日力要收拾它。更不为屈可取。又曾祖道因言伯丰自植立事。先生曰此某知之有未尽。不意伯丰能如此云云。愚于是始知伯丰当时固已卓然自立。不为所屈。而先生初未及知之。故书意如此。及伯丰死后。始乃详知其事。故直卿最后书云然。而又有语类数条之说也。学者见闻不广。固未可硬执一说而轻易以论人也。
伯丰始者犹疑其守之未固。得子约,元德书。又知其自树立之意尤不可及。不幸早死。亦是吾道之衰。味其辞意。似指前书所言之事。而犹以未得详当时事实为恨。后见语类。先生尝曰伯丰好个人。其死可惜。渠与沈(似是沈继祖)是亲近。日力要收拾它。更不为屈可取。又曾祖道因言伯丰自植立事。先生曰此某知之有未尽。不意伯丰能如此云云。愚于是始知伯丰当时固已卓然自立。不为所屈。而先生初未及知之。故书意如此。及伯丰死后。始乃详知其事。故直卿最后书云然。而又有语类数条之说也。学者见闻不广。固未可硬执一说而轻易以论人也。苏东坡子过,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师成之门。以父事之。梁妻死。温与过皆以母礼丧之。衰绖而往哭。夫二人俱以名父之子。粗有文字之名。而乃为此狗彘不若之行。良可痛惜。柳公绰之孙有璨。韩魏公之孙有侂胄。彼皆身任戕贤误国之罪。卒至破坏家法。忝辱父祖。杀身湛宗而不知悟。悲夫。后之为人家子若孙者。可不鉴戒哉。(按语类。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待叔党如亲兄弟云云。余尝见赵氏丛考。辨师成非东坡之子。明有證据。孙觌亦自谓东坡之子。而丛考辨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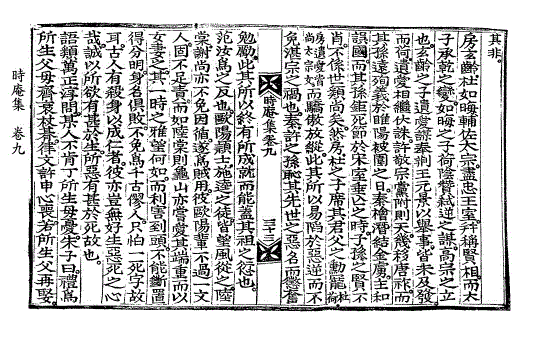 其非。)
其非。)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尽忠王室。并称贤相。而太子承乾之变。如晦之子荷阴赞弑逆之谋。高宗之立也。玄龄之子遗爱谋奉荆王元景以举事。皆未及发。而荷,遗爱相继伏诛。许敬宗党附则天。几移唐祚。而其孙远殉义于睢阳被围之日。秦桧潜结金虏。主和误国。而其孙钜死节于宋室垂亡之时。子孙之贤不肖。不系世类尚矣。然房,杜之子席其君父之勋宠(杜荷,房遗爱皆尚太宗女。)而骄傲放纵。此其所以易陷于恶逆而不免湛宗之祸也。秦,许之孙耻其先世之恶名而惩奋勉励。此其所以终有所成就而能盖其祖之愆也。
范汝为之反也。欧阳颖士,施逵之徒。皆望风从之。陆棠,谢尚亦不免因循。遂为贼用。彼欧阳辈不过一文人。固不足责。而如陆棠则龟山亦尝爱其端重而以女妻之。其一时之雅望何如。而利害到头。不能断置得分明。身名俱败。不免为千古僇人。只怕一死字故耳。古人有杀身以成仁者。彼亦岂无好生恶死之心哉。诚以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故也。
语类万正淳问。某人不肯丁所生母忧。朱子曰。礼为所生父母齐衰杖期。律文许申心丧。若所生父再娶。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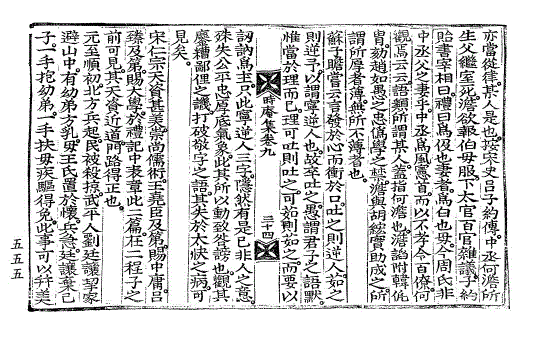 亦当从律。某人是也。按宋史吕子约传。中丞何澹所生父继室死。澹欲报伯母服。下太官百官杂议。子约贻书宰相曰。礼曰为伋也妻者。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中丞为风宪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观焉云云。语类所谓某人。盖指何澹也。澹谄附韩侂胄。劾赵如愚之忠伪学之禁。澹与胡纮实助成之。所谓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者也。
亦当从律。某人是也。按宋史吕子约传。中丞何澹所生父继室死。澹欲报伯母服。下太官百官杂议。子约贻书宰相曰。礼曰为伋也妻者。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中丞为风宪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观焉云云。语类所谓某人。盖指何澹也。澹谄附韩侂胄。劾赵如愚之忠伪学之禁。澹与胡纮实助成之。所谓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者也。苏子瞻尝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愚谓君子之语默。惟当于理而已。理可吐则吐之。可茹则茹之。而要以讱讷为主。只此宁逆人三字。隐然有是己非人之意。殊失公平忠厚底气象。此其所以动致咎谤也。观其鏖糟鄙俚之讥。打破敬字之语。其失于太快之病。可见矣。
宋仁宗天资甚美。崇尚儒术。王尧臣及第。赐中庸。吕臻及第。赐大学。于礼记中表章此二篇。在二程子之前可见。其天资近道。门路得正也。
元至顺初。北方兵起。民被杀掠。武平人刘廷让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怀。兵急。廷让弃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驱得免。此事可以并美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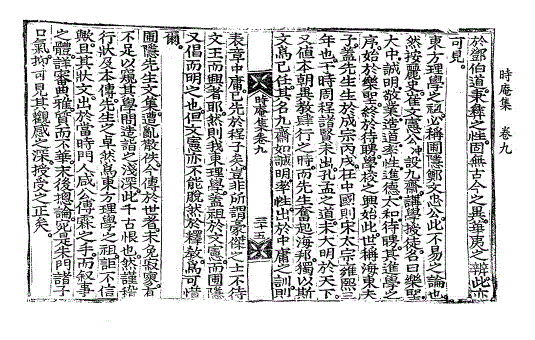 于邓伯道。秉彝之性。固无古今之异。华夷之辨。此亦可见。
于邓伯道。秉彝之性。固无古今之异。华夷之辨。此亦可见。东方理学之祖。必称圃隐郑文忠公。此不易之论也。然按丽史。崔文宪公(冲)设九斋。讲学授徒。名曰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太和,待聘。其进学之序。始于乐圣。终于待聘。学校之兴始此。世称海东夫子。盖先生生于成宗丙戌。在中国则宋太宗雍熙三年也。于时周程诸贤未出。孔孟之道。未大明于天下。又值本朝异教肆行之时。而先生奋起海邦。独以斯文为己任。其名九斋如诚明,率性。出于中庸之训。则表章中庸。已先于程子矣。岂非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者耶。然则我东理学。盖祖于文宪。而圃隐又倡而明之也。但文宪亦不能脱然于释教。为可惜尔。
圃隐先生文集。遭乱散佚。今传于世者。未免寂寥。有不足以窥其学问造诣之浅深。此千古恨也。然谨稽行状及本传。先生之卓然为东方理学之祖。讵不信欤。且其状文。出于当时门人咸公傅霖之手。而叙事之体。详审典雅。质而不华。末后总论。宛是朱门诸子口气。抑可见其观感之深。授受之正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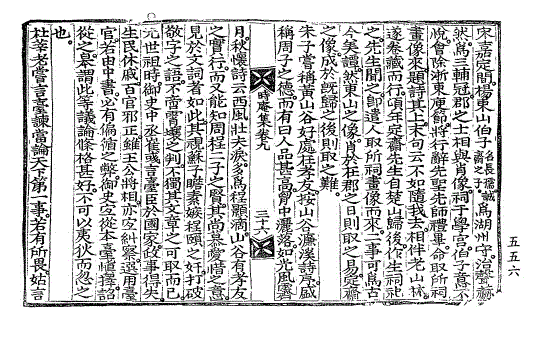 宋嘉定间。杨东山伯子(名长孺。诚斋之子。)为湖州守。治声赫然。为三辅冠。郡之士相与肖像。祠于学宫。伯子意不悦。会除浙东庾节。将行辞先圣先师礼毕。命取所祠画像来。题诗其上。末句云不如随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顷年定斋先生自楚山归后。作生祠祀之。先生闻之。即遣人取所祠画像而来。二事可为古今美谭。然东山之像。肖于在郡之日则取之易。定斋之像。成于既归之后则取之难。
宋嘉定间。杨东山伯子(名长孺。诚斋之子。)为湖州守。治声赫然。为三辅冠。郡之士相与肖像。祠于学宫。伯子意不悦。会除浙东庾节。将行辞先圣先师礼毕。命取所祠画像来。题诗其上。末句云不如随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顷年定斋先生自楚山归后。作生祠祀之。先生闻之。即遣人取所祠画像而来。二事可为古今美谭。然东山之像。肖于在郡之日则取之易。定斋之像。成于既归之后则取之难。朱子尝称黄山谷好处在孝友。按山谷濂溪诗序。盛称周子之德。而有曰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秋怀诗云西风壮夫泪。多为程颢滴。山谷有孝友之实行。而又能知周程二子之贤。其尚慕爱惜之意。见于文词者如此。其视苏子瞻素嫉程颐之奸。打破敬字之语。不啻霄壤之判。不独其文章之可取而已。
元世祖时。御史中丞崔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选用台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循之弊。御史宜从本台慎择。诏从之。皋谓此等议论条格甚好。不可以夷狄而忽之也。
杜莘老尝言台谏当论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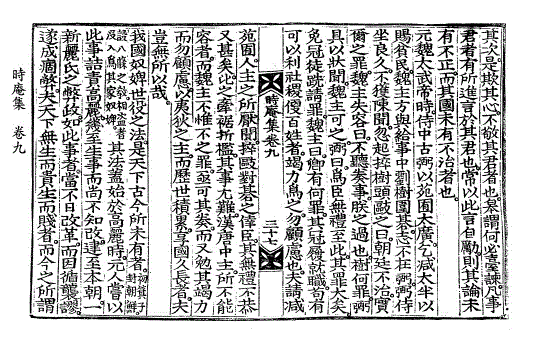 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皋谓何必台谏。凡事君者有所进言于其君也。常以此言自励。则其论未有不正。而其国未有不治者也。
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皋谓何必台谏。凡事君者有所进言于其君也。常以此言自励。则其论未有不正。而其国未有不治者也。元魏太武帝时。侍中古弼以苑囿太广。乞减太半以赐贫民。魏主方与给事中刘树围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获陈闻。忽起捽树头驱之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魏主失容曰。不听奏事。朕之过也。树何罪。弼具以状闻。魏主可之。弼曰。为臣无礼至此。其罪大矣。免冠徒跣请罪。魏主曰。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职。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为之。勿顾虑也。夫请减苑囿。人主之所厌闻。捽驱对棋之倖臣。其无礼不恭又甚矣。比之牵裾折槛。其事尤难。汉唐中主。所不能容者。而魏主不惟不之罪。亟可其奏。而又勉其竭力而勿顾虑。以夷狄之主。而历世积累。享国久长者。夫岂无所以哉。
我国奴婢世役之法。是天下古今所未有者。(初箕子封朝鲜。设八条之教。相盗者没入为其家奴婢。)其法盖始于高丽时。元人尝以此事诘责高丽。几至生事而尚不知改。逮至本朝。一新丽氏之弊政。如此事者。当不日改革。而因循袭谬。遂成痼弊。夫天下无生而贵生而贱者。而今之所谓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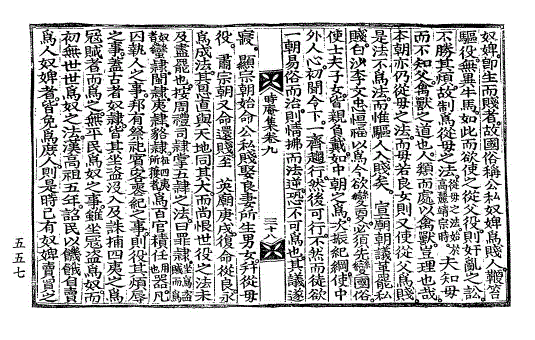 奴婢。即生而贱者。故国俗称公私奴婢为贱人。鞭笞驱役。无异牛马。如此而欲使之从父役。则奸乱之讼。不胜其烦。故制为从母之法。(从母之法。始于高丽靖宗时。)夫知母而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类而处以禽兽。岂理也哉。本朝亦仍从母之法。而母若良女则又使从父为贱。是法不为法。而惟驱人入贱矣。 宣庙朝议革罢私贱。白沙李文忠恒福以为今欲变更。必须先变国俗。使士夫子女。皆亲负戴。如中朝之为。次振纪纲。使中外人心。初闻令下。一齐趋行。然后可行。不然而徒欲一朝易俗而治。则情拂而法逆。恐不可为也。其议遂寝。 显宗朝始命公私贱娶良妻所生男女。并从母役。 肃宗朝又命还贱。至 英庙庚戌。复命从良。永为成法。其恩直与天地同其大。而尚恨世役之法未及尽罢也。按周礼司隶掌五隶之法。曰罪隶,(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蛮隶,闽隶,夷隶,貉隶。(征四夷所获者。)为百官积任(用也)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盖古者奴隶。皆其坐盗没入及诛捕四夷之为寇贼者而为之。无平民为奴之事。虽坐寇盗为奴。而初无世世为奴之法。汉高祖五年。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则是时已有奴婢卖买之
奴婢。即生而贱者。故国俗称公私奴婢为贱人。鞭笞驱役。无异牛马。如此而欲使之从父役。则奸乱之讼。不胜其烦。故制为从母之法。(从母之法。始于高丽靖宗时。)夫知母而不知父。禽兽之道也。人类而处以禽兽。岂理也哉。本朝亦仍从母之法。而母若良女则又使从父为贱。是法不为法。而惟驱人入贱矣。 宣庙朝议革罢私贱。白沙李文忠恒福以为今欲变更。必须先变国俗。使士夫子女。皆亲负戴。如中朝之为。次振纪纲。使中外人心。初闻令下。一齐趋行。然后可行。不然而徒欲一朝易俗而治。则情拂而法逆。恐不可为也。其议遂寝。 显宗朝始命公私贱娶良妻所生男女。并从母役。 肃宗朝又命还贱。至 英庙庚戌。复命从良。永为成法。其恩直与天地同其大。而尚恨世役之法未及尽罢也。按周礼司隶掌五隶之法。曰罪隶,(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蛮隶,闽隶,夷隶,貉隶。(征四夷所获者。)为百官积任(用也)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盖古者奴隶。皆其坐盗没入及诛捕四夷之为寇贼者而为之。无平民为奴之事。虽坐寇盗为奴。而初无世世为奴之法。汉高祖五年。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则是时已有奴婢卖买之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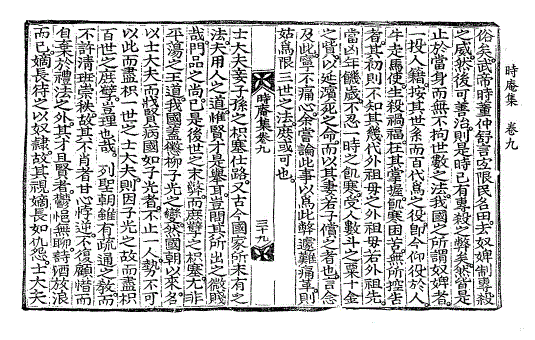 俗矣。武帝时董仲舒言宜限民名田。去奴婢制专杀之威。然后可善治。则是时已有专杀之弊矣。然皆是止于当身而无不拘世数之法。我国之所谓奴婢者。一投人籍。按其世系而百代为之役。即今仰役于人。牛走马使。生杀祸福。在其掌握。饥寒困苦。无所控告者。其初则不知其几代外祖母之外祖母若外祖先。当凶年饥岁。不忍一时之饥寒。受人数斗之粟十金之赀。以延滨死之命。而以其妻若子偿之者也。言念及此。宁不痛心。余尝论此事以为此弊遽难痛革。则姑为限三世之法。庶或可也。
俗矣。武帝时董仲舒言宜限民名田。去奴婢制专杀之威。然后可善治。则是时已有专杀之弊矣。然皆是止于当身而无不拘世数之法。我国之所谓奴婢者。一投人籍。按其世系而百代为之役。即今仰役于人。牛走马使。生杀祸福。在其掌握。饥寒困苦。无所控告者。其初则不知其几代外祖母之外祖母若外祖先。当凶年饥岁。不忍一时之饥寒。受人数斗之粟十金之赀。以延滨死之命。而以其妻若子偿之者也。言念及此。宁不痛心。余尝论此事以为此弊遽难痛革。则姑为限三世之法。庶或可也。士大夫妾子孙之枳塞仕路。又古今国家所未有之法。夫用人之道。惟贤才是举耳。岂问其所出之微贱哉。门品之尚。已是后世之末弊。而庶孽之枳塞。尤非平荡之王道。我国盖惩柳子光之变。然国朝以来。名以士大夫而戕贤病国如子光者。不止一人。势不可以此而尽枳一世之士大夫。则因子光之故而尽枳百世之庶孽。岂理也哉。 列圣朝虽有疏通之教。而不许清班崇秩。故其不肖者甘心悖逆。不复顾惜。而自弃于礼法之外。其才且贤者。郁悒无聊。诗酒放浪而已。嫡长待之以奴隶。故其视嫡长如仇怨。士大夫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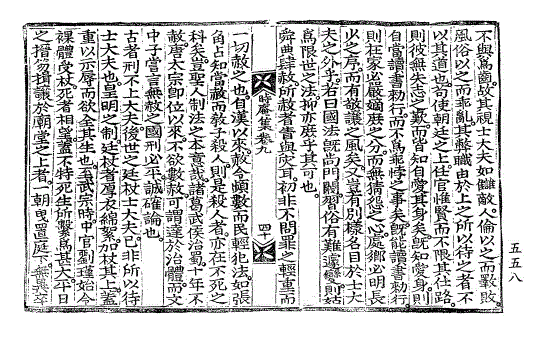 不与为齿。故其视士大夫如雠敌。人伦以之而斁败。风俗以之而乖乱。其弊职由于上之所以待之者不以其道也。苟使朝廷之上。任官惟贤而不限其仕路。则彼无失志之叹。而皆知自爱其身矣。既知爱身。则自当读书敕行。而不为乖悖之事矣。既能读书敕行。则在家必严嫡庶之分。而无猜怨之心。处乡必明长少之序。而有敬让之风矣。又岂有别样名目于士大夫之外乎。若曰国法既尚门阀。习俗有难遽变。则姑为限世之法。抑亦庶乎其可也。
不与为齿。故其视士大夫如雠敌。人伦以之而斁败。风俗以之而乖乱。其弊职由于上之所以待之者不以其道也。苟使朝廷之上。任官惟贤而不限其仕路。则彼无失志之叹。而皆知自爱其身矣。既知爱身。则自当读书敕行。而不为乖悖之事矣。既能读书敕行。则在家必严嫡庶之分。而无猜怨之心。处乡必明长少之序。而有敬让之风矣。又岂有别样名目于士大夫之外乎。若曰国法既尚门阀。习俗有难遽变。则姑为限世之法。抑亦庶乎其可也。舜典肆赦所赦。者眚与灾耳。初非不问罪之轻重而一切赦之也。自汉以来。赦令频数而民轻犯法。如张角占知当赦而教子杀人。则是杀人者。亦在不死之科矣。岂圣人制法之本意哉。诸葛武侯治蜀。十年不赦。唐太宗即位以来。不欲数赦。可谓达于治体。而文中子尝言无赦之国刑必平。诚确论也。
古者刑不上大夫。后世之廷杖士大夫。已非所以待士大夫也。皇明之制。廷杖者厚衣绵絮。加杖其上。盖重以示辱而欲全其生也。至武宗时。中官刘瑾始令裸体受杖。死者相望。盖不特死生所系为甚大。平日之搢笏揖让于庙堂之上者。一朝曳置庭下。无异卒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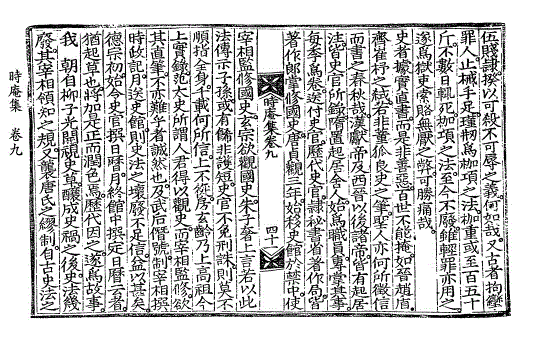 伍贱隶。揆以可杀不可辱之义。何如哉。又古者拘挛罪人。止械手足。瑾刱为枷项之法。枷重或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枷项之法。至今不废。虽轻罪亦用之。遂为狱吏索赂无厌之弊。可胜痛哉。
伍贱隶。揆以可杀不可辱之义。何如哉。又古者拘挛罪人。止械手足。瑾刱为枷项之法。枷重或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枷项之法。至今不废。虽轻罪亦用之。遂为狱吏索赂无厌之弊。可胜痛哉。史者据实直书。而是非善恶。百世不能掩。如晋赵盾,齐崔杼之弑。若非董狐良史之笔。圣人亦何所徵信而书之春秋哉。汉献帝及西晋以后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录。隋置起居舍人。始为职员。专掌其事。每季为卷。送付史官。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唐贞观三年。始移史馆于禁中。使宰相监修国史。玄宗欲观国史。朱子奢上言若以此法传示子孙。或有饰非护短。史官不免刑诛。则莫不顺指全身。千载何所信。上不从。房玄龄乃上高祖今上实录。范太史所谓人君得以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者诚然也。及武后僭号。制宰相撰时政记。月送史馆。则史法之坏废不足信。益以甚矣。德宗初。始令史官撰日历。月终馆中撰定日历云者。犹起草也。将加是正而润色焉。历代因之。遂为故事。我 朝自柳子光开视史草。酿成史祸之后。史法几废。其宰相领知之规。又袭唐氏之缪制。自古史法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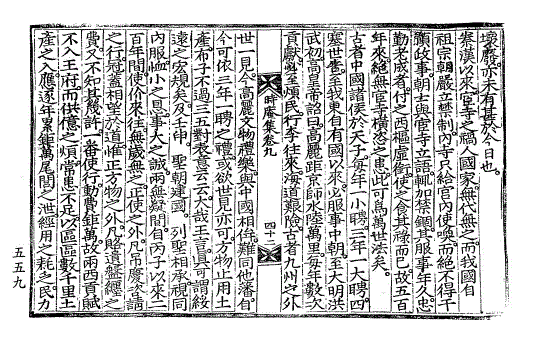 坏废。亦未有甚于今日也。
坏废。亦未有甚于今日也。秦汉以来。宦寺之祸人国家。无代无之。而我国自 祖宗朝严立禁制。内寺只给宫内使唤。而绝不得干预政事。朝士与宦寺立语。辄加禁锢。其服事年久。忠勤老成者。付之西枢虚衔。使之食其禄而已。故五百年来。绝无宦寺横恣之患。此可为万世法矣。
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四塞世告。至我东自有国以来。必服事中朝。至大明洪武初。高皇帝诏曰。高丽距京师水陆万里。每年数次贡献。必至烦民。行李往来。海道艰险。古者九州之外世一见。今高丽文物礼乐。与中国相侔。难同他藩。自今可依三年一聘之礼。或欲世见亦可。方物止用土产。布子不过三五对表意云云。大哉王言。真可谓绥远之宏规矣。及壬申。 圣朝建国。 列圣相承。视同内服。恤小之恩。事大之诚。两无疑间。自丙子以来二百年间。使价来往。无岁无之。正使之外。凡吊庆咨请之行。冠盖相望于道。惟正方物之外。凡赂遗盘缠之费。又不知其几许。一番使行。动费钜万。故两西贡赋不入王府。而供亿之烦。常患不足。以区区数千里土产之入。应逐年累钜万尾闾之泄。经用之耗乏。民力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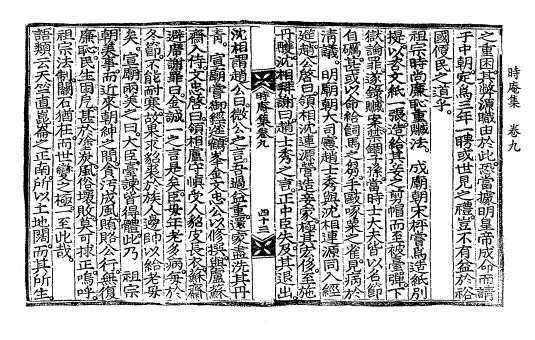 之重困。其弊源职由于此。恐当据明皇帝成命而请于中朝。定为三年一聘或世见之礼。岂不有益于裕国便民之道乎。
之重困。其弊源职由于此。恐当据明皇帝成命而请于中朝。定为三年一聘或世见之礼。岂不有益于裕国便民之道乎。祖宗时尚廉耻重赃法。 成庙朝宋枰尝为造纸别提。以咨文纸一张。造给其妾之剪帽而至被台弹。下狱论罪。遂录赃案。禁锢子孙。当时士大夫皆以名节自砺。甚或以命给饲马之刍。手驱啄粟之雀。见病于清议。 明庙朝大司宪赵士秀与沈相连源同入经筵。赵公启曰。领相沈连源营造妾家。极其宏侈。至施丹雘。沈相拜谢曰。赵士秀之言。正中臣失。及其退出。沈相谓赵公曰。微公之言。吾过益重。还家尽洗其丹青。 宣庙尝御经筵。鹤峰金文忠公以修撰。与卢苏斋入侍。文忠启曰。领相卢守慎受人貂皮长衣。苏斋避席谢罪曰。金诚一之言是矣。臣母年老多病。每于冬节。不能耐寒。故果求貂裘于族人边帅以给老母矣。 宣庙两美之曰。大臣,台谏皆得体。此乃 祖宗朝美事。而近来朝绅之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无复廉耻。民生困厄。甚于涂炭。风俗坏败。莫可救正。呜呼。祖宗法制。关石犹在。而世变之极。一至此哉。
语类云天竺直昆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阔。而其所生。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0L 页
 亦多异人。又曰佛国靠得昆崙山后。那里却暖。四方蛮夷。都不晓人事。那里人却理会得一般道理。那里人也大。故峣崎云云。观此则西域诸国人才之异。盖因其地气之阳明也。近岁屡有异样船浮在海中。往来如飞。其船制广大精致。殆非人工。其中又多珍诡之观。自称大佛郎国人。所称佛郎国者。无或语类所谓佛国者耶。
亦多异人。又曰佛国靠得昆崙山后。那里却暖。四方蛮夷。都不晓人事。那里人却理会得一般道理。那里人也大。故峣崎云云。观此则西域诸国人才之异。盖因其地气之阳明也。近岁屡有异样船浮在海中。往来如飞。其船制广大精致。殆非人工。其中又多珍诡之观。自称大佛郎国人。所称佛郎国者。无或语类所谓佛国者耶。天地之大势。西北高东南下。而日本国诸山。皆发祖于东北。故其地皆东高而西下。殆别开区域于幅员之外者也。
我东之见称于中国旧矣。圣人尝欲居九夷。尔雅云太平之人仁。说者以九夷太平。皆为东夷。班固汉书以为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唐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夫孔子之时。去箕子东来。已六百年所。班固之时。当三韩始造之日。其风气贸贸。人文未辟。而圣人有欲居之言。史氏赞俗尚之美。至于唐宋则为罗丽之世。当时风气人文。虽曰渐就开明。而佛道肆行。儒教未阐。丧纪之废坏。婚娶之渎乱。未免夷虏之风。而犹以文物礼乐之邦。见称于华夏。使唐宋诸大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1H 页
 家先生得见我朝礼樂文物之美。学问教化之盛。宁不兴周礼尽在之叹乎。(语类或言高丽风俗之美。朱子以为犹有夷狄之风。按高丽时国婚不避同姓期功之亲。士大夫多不行三年之丧。朱子所谓夷狄之风。盖指此等事也。)大明一统志所载我国风俗。多鄙诡不经之言。其诬甚矣。
家先生得见我朝礼樂文物之美。学问教化之盛。宁不兴周礼尽在之叹乎。(语类或言高丽风俗之美。朱子以为犹有夷狄之风。按高丽时国婚不避同姓期功之亲。士大夫多不行三年之丧。朱子所谓夷狄之风。盖指此等事也。)大明一统志所载我国风俗。多鄙诡不经之言。其诬甚矣。宋徽宗政和七年。高丽使李资谅至汴京。帝赐宴睿谋殿。密谕曰。闻汝国与女真接壤。后岁来朝。盍招引数人偕来。资谅奏曰。女真人面兽心。夷獠中最为贪丑。不可通上国。宋倖臣闻之曰。女真珍奇杂出。高丽尝交通贸易。不欲分利他国。故沮之。不必借高丽。可遣一价招致。诏马政浮海如金。致书请地。马政以金散睹来。后又诏马政如金。报师期许岁币。遂与金合兵灭辽而分其地。驯致靖康之变。噫。向使宋朝君臣。信听资谅之言。绝不与金相通而无渝契丹之盟好。则金虏虽曰强悍。疆域殊绝。虚实莫侦。则渠何敢生心于中国乎。倖臣之一言诳惑。已兆亡宋之端。而童贯,蔡京之徒。从而成之。此千古志士之扼腕处也。
宁海府治南五里。有地名松岘。我 世宗时。岘南地火。昼夜有烟气而不见火光。投以木皆燃。虽大雨不灭。半月而熄。 成宗甲辰亦然。或云下有石硫黄而掘地不得。按宋史云北庭北山中出䃃砂。山中常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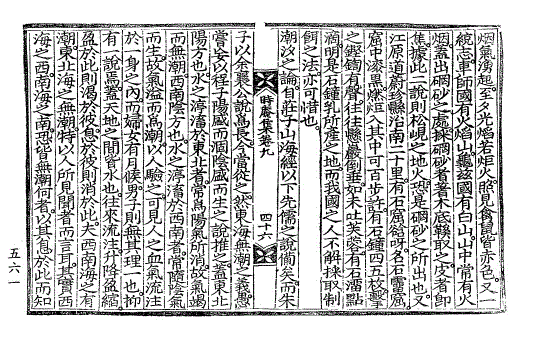 烟气涌起。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色。又一统志。车师国有火焰山。龟玆国有白山。山中常有火烟。盖出䃃砂之处。采䃃砂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据此二说则松岘之地火。恐是䃃砂之所出也。又江原道蔚珍县治南二十里。有石窟谽呀。名石霤窟。窟中漆黑。燃炬入其中可百步许。有石钟四五枚。击之铿鍧有声。往往悬岩倒垂。如未吐芙蓉。有石溜点滴。明是石钟乳所产之地。而我国之人不解采取制饵之法。亦可惜也。
烟气涌起。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色。又一统志。车师国有火焰山。龟玆国有白山。山中常有火烟。盖出䃃砂之处。采䃃砂者著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据此二说则松岘之地火。恐是䃃砂之所出也。又江原道蔚珍县治南二十里。有石窟谽呀。名石霤窟。窟中漆黑。燃炬入其中可百步许。有石钟四五枚。击之铿鍧有声。往往悬岩倒垂。如未吐芙蓉。有石溜点滴。明是石钟乳所产之地。而我国之人不解采取制饵之法。亦可惜也。潮汐之论。自庄子山海经以下先儒之说备矣。而朱子以余襄公说为长。今当从之。然东海无潮之义。愚尝妄以程子阳盛而涸阴盛而生之说推之。盖东北阳方也。水之渟滀于东北者。常为阳气所消。故气竭而无潮。西南阴方也。水之渟滀于西南者。常随阴气而生。故气溢而为潮。以人验之。可见人之血气流注于一身之内。而妇女有月候。男子则无其理一也。抑有一说焉。盖天地之间皆水也。往来流注。升降盈缩。盈于此则渴于彼。息于彼则消于此。夫西南海之有潮。东北海之无潮。特以人所见闻者而言耳。其实西海之西。南海之南。恐皆无潮何者。以其息于此而知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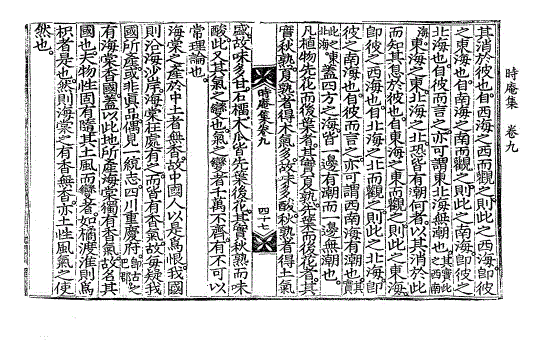 其消于彼也。自西海之西而观之。则此之西海。即彼之东海也。自南海之南而观之。则此之南海。即彼之北海也。自彼而言之。亦可谓东北海无潮也。(其实此之西南海。)东海之东。北海之北。恐皆有潮何者。以其消于此而知其息于彼也。自东海之东而观之。则此之东海。即彼之西海也。自北海之北而观之。则此之北海。即彼之南海也。自彼而言之。亦可谓西南海有潮也。(其实此之东北海。)盖四方之海。皆一边有潮而一边无潮也。
其消于彼也。自西海之西而观之。则此之西海。即彼之东海也。自南海之南而观之。则此之南海。即彼之北海也。自彼而言之。亦可谓东北海无潮也。(其实此之西南海。)东海之东。北海之北。恐皆有潮何者。以其消于此而知其息于彼也。自东海之东而观之。则此之东海。即彼之西海也。自北海之北而观之。则此之北海。即彼之南海也。自彼而言之。亦可谓西南海有潮也。(其实此之东北海。)盖四方之海。皆一边有潮而一边无潮也。凡植物先花而后叶者。其实夏熟。先叶而后花者。其实秋熟。夏熟者得木气多。故味多酸。秋熟者得土气盛。故味多甘。石榴,木瓜皆先叶后花。其实秋熟而味酸。此又其气之变也。气之变者千万不齐。有不可以常理论也。
海棠之产于中土者无香。故中国人以是为恨。我国则沿海沙岸。海棠在处有之。而皆有香气。故每疑我国所产。或非真品。偶见一统志。四川重庆府。(即古之巴郡。)有海棠香国。盖以此地所产海棠独有香气。故名其国也。夫物性固有随其土风而变者。如橘渡淮则为枳者是也。然则海棠之有香无香。亦土性风气之使然也。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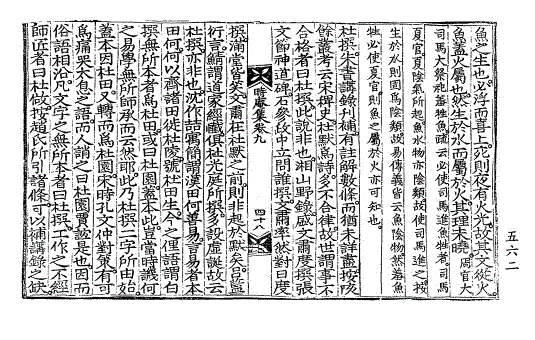 鱼之生也。必浮而喜上。死则夜有火光。故其文从火。鱼盖火属也。然生于水而属于火。其理未晓。(周官大司马大祭祀羞牲鱼。疏云必使司马进鱼牲者。司马夏官。夏阴气所起。鱼水物亦阴类。故使司马进之。按生于水则固为阴类。故易传义皆云鱼阴物。然羞鱼牲必使夏官。则鱼之属于火亦可知也。)
鱼之生也。必浮而喜上。死则夜有火光。故其文从火。鱼盖火属也。然生于水而属于火。其理未晓。(周官大司马大祭祀羞牲鱼。疏云必使司马进鱼牲者。司马夏官。夏阴气所起。鱼水物亦阴类。故使司马进之。按生于水则固为阴类。故易传义皆云鱼阴物。然羞鱼牲必使夏官。则鱼之属于火亦可知也。)杜撰。朱书讲录刊补。有注解数条。而犹未详尽。按陔馀丛考云宋稗史。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世谓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说非也。湘山野录。盛文肃度撰张文节神道碑。石参政中立问谁撰。文肃率然对曰度撰。满堂皆笑。文肃在杜默之前。则非起于默矣。吕蓝衍言。鲭谓道家经忏。俱杜光庭所撰。多设虚诞故云杜撰。亦非也。沈作哲寓简谓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俚语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盖本此。岂当时讥何之易学无所师承而云然耶。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盖本因杜田。又转而为杜园。宋时孔文仲对策。有可为痛哭太息之语。而人诮之曰杜园贾谊是也。因而俗语相沿。凡文字之无所本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经师匠者曰杜做。按赵氏所引诸条。可以补讲录之缺。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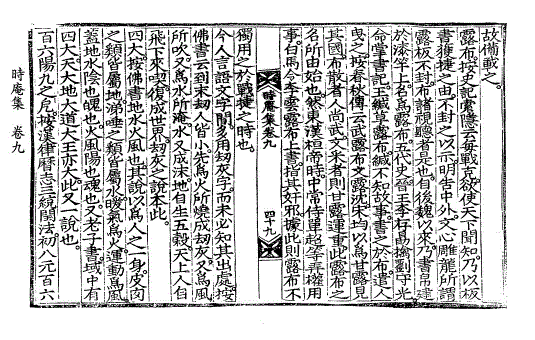 故备载之。
故备载之。露布。按史记索隐云每战克。欲使天下闻知。乃以板书获捷之由。不封之以示。明告中外。文心雕龙所谓露板不封。布诸视听者是也。自后魏以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名为露布。五代史。晋王李存勖擒刘守光。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按春秋传云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以为甘露见其国。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则甘露运重。此露布之名所由始也。然东汉桓帝时。中常侍单超等弄权用事。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指其奸邪。据此则露布不独用之于战捷之时也。
今人言语文字间。多用劫灰字。而未必知其出处。按佛书云到末劫人皆小。先为火所烧成劫灰。又为风所吹。又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谷。天上人自飞下来吃。复成世界。劫灰之说本此。
四大。按佛书地水火风也。其说以为人之一身。皮肉之类皆属地。涕唾之类皆属水。暖气为火。运动为风。盖地水阴也魄也。火风阳也魂也。又老子书。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此又一说也。
百六阳九之厄。按汉律历志三统闰法。初八元百六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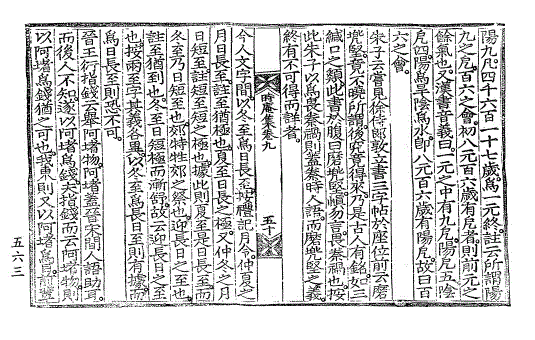 阳九。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终。注云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初八元百六岁有厄者。则前元之馀气也。又汉书音义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阳厄五。阴厄四。阳为旱阴为水。即八元百六岁有阳厄。故曰百六之会。
阳九。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终。注云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初八元百六岁有厄者。则前元之馀气也。又汉书音义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阳厄五。阴厄四。阳为旱阴为水。即八元百六岁有阳厄。故曰百六之会。朱子云尝见徐侍郎敦立书三字帖于座位前云磨兜坚。竟不晓所谓。后究竟得来。乃是古人有铭。如三缄口之类。此书于腹曰磨兜坚。慎勿言。畏秦祸也。按此朱子以为畏秦祸则盖秦时人语。而磨兜坚之义。终有不可得而详者。
今人文字间。以冬至为日长至。按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长至。注至犹极也。夏至日长之极。又仲冬之月日短至。注短至短之极也。据此则夏至是日长至。而冬至乃日短至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注至犹到也。冬至日短极而渐舒。故云迎长日之至也。按两至字其义各异。以冬至为长日至则有据。而为日长至则恐不可。
晋王衍指钱云举阿堵物。阿堵盖晋宋间人语助耳。而后人不知。遂以阿堵为钱。夫指钱而云阿堵物。则以阿堵为钱犹之可也。我东则又以阿堵为目。前辈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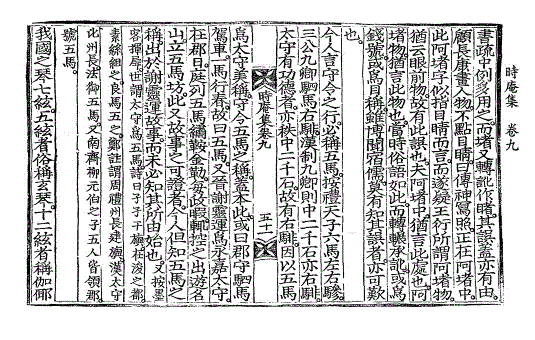 书疏中例多用之。而堵又转讹作睹。其误盖亦有由。顾长康画人物。不点目睛。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此阿堵字似指目睛而言。而遂疑王衍所谓阿堵物。犹云眼前物。故有此误也。夫阿堵中。犹言此处也。阿堵物。犹言此物也。当时俗语如此。而转辗承讹。或为钱号。或为目称。虽博闻宿儒。莫有知其误者。亦可叹也。
书疏中例多用之。而堵又转讹作睹。其误盖亦有由。顾长康画人物。不点目睛。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此阿堵字似指目睛而言。而遂疑王衍所谓阿堵物。犹云眼前物。故有此误也。夫阿堵中。犹言此处也。阿堵物。犹言此物也。当时俗语如此。而转辗承讹。或为钱号。或为目称。虽博闻宿儒。莫有知其误者。亦可叹也。今人言守令之行。必称五马。按礼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右騑。汉制九卿则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有功德者。亦秩中二千石。故有右騑。因以五马为太守美称。守令五马之称。盖本此。或曰郡守驷马驾车。一马行春。故曰五马。又晋谢灵运为永嘉太守。在郡日。庭列五马绣鞍金勒。每政暇。辄控之出游名山。立五马坊。此又故事之可證者。今人但知五马之称。出于谢灵运故事。而未必知其所由始也。(又按墨客挥犀。世谓太守为五马。诗曰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旟。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又南齐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领郡。号五马。)
我国之琴七弦。五弦者俗称玄琴。十二弦者称伽倻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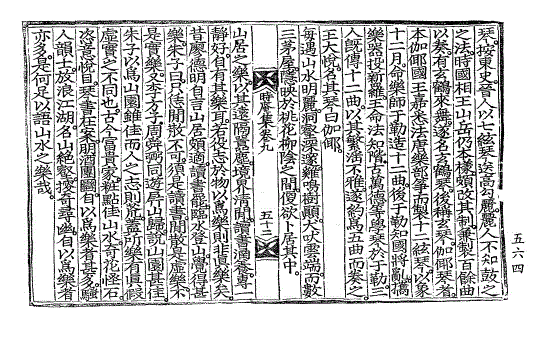 琴。按东史。晋人以七弦琴送高勾丽。丽人不知鼓之之法。时国相王山岳仍本样。颇改其制。兼制百馀曲以奏。有玄鹤来舞。遂名玄鹤琴。后称玄琴。伽倻琴者。本伽倻国王嘉悉法唐乐部筝而制十二弦琴。以象十二月。命乐师于勒造十二曲。后于勒知国将乱。携乐器投新罗。王命法知阶,古万德等学琴于于勒。三人既传十二曲。以其繁淫不雅。遂约为五曲而奏之。王大悦。名其琴曰伽倻。
琴。按东史。晋人以七弦琴送高勾丽。丽人不知鼓之之法。时国相王山岳仍本样。颇改其制。兼制百馀曲以奏。有玄鹤来舞。遂名玄鹤琴。后称玄琴。伽倻琴者。本伽倻国王嘉悉法唐乐部筝而制十二弦琴。以象十二月。命乐师于勒造十二曲。后于勒知国将乱。携乐器投新罗。王命法知阶,古万德等学琴于于勒。三人既传十二曲。以其繁淫不雅。遂约为五曲而奏之。王大悦。名其琴曰伽倻。每遇山水明丽。洞壑深邃。鸡鸣树颠。犬吠云端。而数三茅屋。隐映于桃花柳阴之间。便欲卜居其中。
山居之乐。以其远隔嚣尘。境界清閒。读书涵养。专一静好。自有其乐耳。若役志于物以为乐则非真乐矣。昔廖德明自言山居颇适。读书罢。临水登山。觉得甚乐。朱子曰。只恁閒散不可。须是读书。閒散是虚乐。不是实乐。又李方子,周舜弼同游屏山归。说山园甚佳。朱子以为山园虽佳而人之志则荒。盖所乐有真假虚实之不同也。古今富贵家。妆点佳山水。奇花怪石。恣意悦目。琴书在案。朋酒团圞。自以为乐者甚多。骚人韵士。放浪江湖。名山绝壑。搜奇寻幽。自以为乐者亦多。是何足以语山水之乐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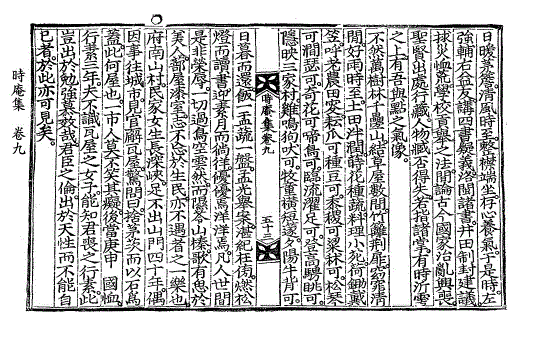 日暖茅檐。清风时至。整襟端坐。存心养气。于是时。左强辅右益友。讲四书疑义。洛闽诸书。井田制封建议。救灾恤荒。学校贡举之法。间论古今国家治乱兴丧。圣贤出处行藏。人物臧否得失。若指诸掌。有时沂雩之上。有吾与点之气像。
日暖茅檐。清风时至。整襟端坐。存心养气。于是时。左强辅右益友。讲四书疑义。洛闽诸书。井田制封建议。救灾恤荒。学校贡举之法。间论古今国家治乱兴丧。圣贤出处行藏。人物臧否得失。若指诸掌。有时沂雩之上。有吾与点之气像。不然万树林千叠山。结草屋数间。竹篱荆扉。窈窕清閒。好雨时至。土田泮润。莳花种蔬。料理小苑。荷锄戴笠。呼老农田叟。耘瓜可种豆可。黍稷可粱秫可。松琴可涧瑟可。奇花可啼鸟可。临流濯足可。登高骋眺可。隐映三家村。鸡鸣狗吠可。牧童横短篴。夕阳牛背可。日暮而还。饭一盂蔬一盘。孟光举案。湛纪在傍。燃松灯而读书。迎素月而徜徉。优优焉洋洋焉。凡人世间是非荣辱。一切过鸟空云然。而隰苓山榛。歌有思于美人。蔀屋漆室。志不忘于生民。亦不遇者之一乐也。
府南山村。民家女生长深峡。足不出山门四十年。偶因事往城市。见官廨瓦屋。惊问曰。舍茅茨而以石为盖。此何屋也。一市人莫不笑其痴。后当庚申 国恤。行素三年。夫不识瓦屋之女子。能知君丧之行素。此岂出于勉强慕效哉。君臣之伦。出于天性而不能自已者。于此亦可见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5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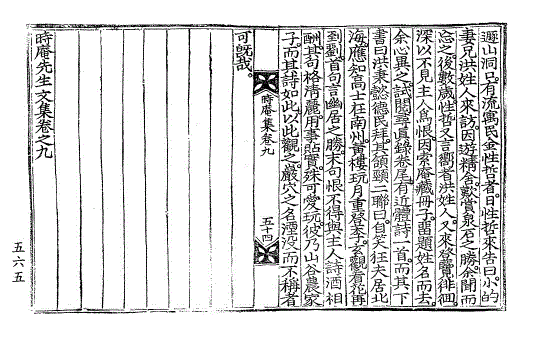 遁山洞口。有流寓民金性哲者。日性哲来告曰。小的妻兄洪姓人来访。因游精舍。叹赏泉石之胜。余闻而忘之。后数岁。性哲又言向者洪姓人。又来登览徘徊。深以不见主人为恨。因索庵藏册子。留题姓名而去。余心异之。试阅寻真录卷尾。有近体诗一首。而其下书曰洪秉懿德民拜。其颔颈二联曰。自笑狂夫居北海。应知高士在南州。黄楼玩月重登李。玄观看花再到刘。首句言幽居之胜。末句恨不得与主人诗酒相酬。其句格清丽。用事贴实。殊可爱玩。彼乃山谷农家子。而其诗如此。以此观之。岩穴之名湮没而不称者可既哉。
遁山洞口。有流寓民金性哲者。日性哲来告曰。小的妻兄洪姓人来访。因游精舍。叹赏泉石之胜。余闻而忘之。后数岁。性哲又言向者洪姓人。又来登览徘徊。深以不见主人为恨。因索庵藏册子。留题姓名而去。余心异之。试阅寻真录卷尾。有近体诗一首。而其下书曰洪秉懿德民拜。其颔颈二联曰。自笑狂夫居北海。应知高士在南州。黄楼玩月重登李。玄观看花再到刘。首句言幽居之胜。末句恨不得与主人诗酒相酬。其句格清丽。用事贴实。殊可爱玩。彼乃山谷农家子。而其诗如此。以此观之。岩穴之名湮没而不称者可既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