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x 页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杂著
杂著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2H 页
 困勉录
困勉录孟子所引诗书之文。皆载今诗书中。而其引孔子之言。如道之仁与不仁。心之操存舍亡。沧浪自取之戒。去鲁迟迟之叹。七篇外无见处。孟子固非凿空撰出。则是当时必有可据之书。而今皆不得见焉。是可恨也。其幸而存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易卦六爻。第一爻第六爻。不言一六而称初上者。所以明卦画之始于下而终于上也。其不称九初九上。如九二九五之例。而变文称初九上九者。以位之在下者为初。居终者为上。故先言位而后言爻也。九二九三九四九五。若从初九上九之例。而称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则嫌于积实之数。故先言爻而后言位也。六二六三六四六五放此。
乾卦圣人之事也。而初九首揭潜字。九三言惕字。上九戒亢字。用九申之以无首吉三字。圣人之意可见矣。
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传以执言为奉辞。本义以执为搏执。而以言为语辞。按利执云者。利于执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2L 页
 禽也。如解之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之义也。若以利执言。解作利奉辞。则文义却似生硬。且奉辞讨罪。恐非可言于田禽也。当以本义搏执之训为正。而但以言字为语辞则亦恐未然。盖尝反复潜玩。而觉得言字恐是吉字之误也。何以知其然也。易中诸卦言吉则不言无咎。言无咎则不言吉。盖有吉而不免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尽善也。师卦言吉无咎者三。卦辞之丈人吉无咎。九二之在师中吉无咎及六五之田有禽利执吉无咎是也。卦辞之吉无咎者。盖兵者凶器也。师者毒民也。凶器也。故难保其吉。毒民也。故易致凶咎。必有丈人之德然后。吉且无咎也。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夫为君而尽其任将之道然后。方可谓尽善也。为将而尽其为将之道然后。亦可谓尽善也。九二之丈人。尽其行师之道。故吉而无咎。则六五之君。尽其兴师之道者。抑岂非吉而无咎者乎。以言为吉而后。理顺义得而无龃龉生硬之患矣。言与吉恐是字相似而误也。蒙陋蔑识。妄疑大贤之训释。极知僭踰。姑私记之以俟百世。
禽也。如解之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之义也。若以利执言。解作利奉辞。则文义却似生硬。且奉辞讨罪。恐非可言于田禽也。当以本义搏执之训为正。而但以言字为语辞则亦恐未然。盖尝反复潜玩。而觉得言字恐是吉字之误也。何以知其然也。易中诸卦言吉则不言无咎。言无咎则不言吉。盖有吉而不免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尽善也。师卦言吉无咎者三。卦辞之丈人吉无咎。九二之在师中吉无咎及六五之田有禽利执吉无咎是也。卦辞之吉无咎者。盖兵者凶器也。师者毒民也。凶器也。故难保其吉。毒民也。故易致凶咎。必有丈人之德然后。吉且无咎也。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夫为君而尽其任将之道然后。方可谓尽善也。为将而尽其为将之道然后。亦可谓尽善也。九二之丈人。尽其行师之道。故吉而无咎。则六五之君。尽其兴师之道者。抑岂非吉而无咎者乎。以言为吉而后。理顺义得而无龃龉生硬之患矣。言与吉恐是字相似而误也。蒙陋蔑识。妄疑大贤之训释。极知僭踰。姑私记之以俟百世。易大传曰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此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3H 页
 后世互卦之说所由起也。六十二卦。互体止为十六卦者何也。盖互体只取中四画。而四画为十六故也。(三画而为八卦。四画而为十六。)六十四卦中。正对者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而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六卦互体。不出此六卦之内。(坎互为颐。离互为大过。颐互为小过。大过互为中孚。中孚互颐。小过互大过。)又十六卦互体。亦皆反对。其亦妙矣。(如屯互为剥。蒙互为复。而剥复反对。馀卦皆然。)六十四卦中。乾坤独无互体。盖乾坤父母之道。其尊无对故也。既济,未济反对。及互卦皆水火相衔。(既济反对互体皆为未济。未济反对互体皆为既济。)盖水火生民之大用。而必相须以为用故也。
后世互卦之说所由起也。六十二卦。互体止为十六卦者何也。盖互体只取中四画。而四画为十六故也。(三画而为八卦。四画而为十六。)六十四卦中。正对者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而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六卦互体。不出此六卦之内。(坎互为颐。离互为大过。颐互为小过。大过互为中孚。中孚互颐。小过互大过。)又十六卦互体。亦皆反对。其亦妙矣。(如屯互为剥。蒙互为复。而剥复反对。馀卦皆然。)六十四卦中。乾坤独无互体。盖乾坤父母之道。其尊无对故也。既济,未济反对。及互卦皆水火相衔。(既济反对互体皆为未济。未济反对互体皆为既济。)盖水火生民之大用。而必相须以为用故也。三十六宫。固主反对说。然不特反对为然。八纯卦外。五十六卦交错颠倒。亦为二十八卦。(如山雷颐反为雷山小过,风泽中孚反为泽风大过之类。)并八纯卦为三十六宫。且以卦画观之。非但八纯卦阴阳画合为三十六。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复,姤相对。颐,大过相对。而复卦阴阳画十一。姤卦阴阳画七。合为十有八。颐卦阴阳画十。大过卦阴阳画八。亦合为十有八。四卦之画。通为三十六。乾,坤相对。夬,剥相对。而乾卦阳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3L 页
 画六。坤卦阴画十二。合为十有八。夬卦阴阳画七。剥卦阴阳画十一。亦合为十有八。四卦之画通为三十六。馀皆仿此。而四卦之画合为三十六者。凡一十有六。十六者亦四画之数也。(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为四画者十六。)四其四而为十六。四其十六而为六十四。其亦妙矣哉。
画六。坤卦阴画十二。合为十有八。夬卦阴阳画七。剥卦阴阳画十一。亦合为十有八。四卦之画通为三十六。馀皆仿此。而四卦之画合为三十六者。凡一十有六。十六者亦四画之数也。(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为四画者十六。)四其四而为十六。四其十六而为六十四。其亦妙矣哉。洪范皇极传。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至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一节。皆指民而言。此虽箕子告武王之辞。当转作武王诏其民之语。看上下文义。始活络通贯。其意若曰惟尔庶民。无有偏陂好恶。以遵王之义王之道可也。民心无有偏党反侧之私。则王道本自平荡正直而可以会而归也。有极指王之道也。会而归指民而言也。朱子皇极辨。已分明说了。而蔡传亦然。特读者未察而泛以为箕子告武王之言。故主人君说。失其旨矣。
召南驺虞章朱子集传。驺虞兽名。不食生物者。吁嗟乎驺虞。叹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则真所谓驺虞矣。其语意与首篇麟趾章注所谓言之不足。又嗟叹之。言是乃麟也之意相类。盖本小序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之说也。皋每疑之。夫以兽名训驺虞。则此一句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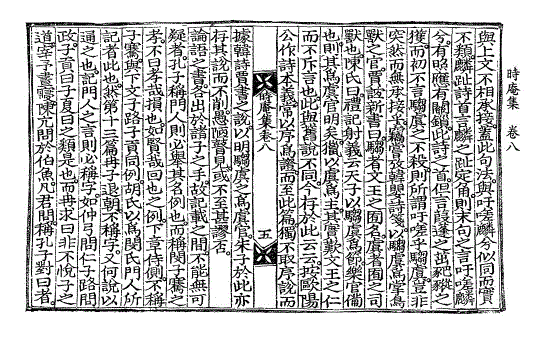 与上文不相承接。盖此句法。与吁嗟麟兮似同而实不类。麟趾诗首言麟之趾定角。则末句之言吁嗟麟兮。有照应有关锁。此诗之首。但言葭蓬之茁豝豵之获。而初不言驺虞之不杀。则所谓吁嗟乎驺虞。岂非突然而无承接乎。窃尝考韩婴诗笺。以驺虞为掌鸟兽之官。贾谊新书曰。驺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兽也。陈氏曰。礼记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则其为虞官明矣。猎以虞为主。其实叹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与旧说不同。今存于此云云。按欧阳公作诗本义。常以序为證。而至此篇。独不取序说而据韩诗贾书之说。以明驺虞之为虞官。朱子于此亦存其说而不削。愚陋瞽见。或不至甚谬否。
与上文不相承接。盖此句法。与吁嗟麟兮似同而实不类。麟趾诗首言麟之趾定角。则末句之言吁嗟麟兮。有照应有关锁。此诗之首。但言葭蓬之茁豝豵之获。而初不言驺虞之不杀。则所谓吁嗟乎驺虞。岂非突然而无承接乎。窃尝考韩婴诗笺。以驺虞为掌鸟兽之官。贾谊新书曰。驺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兽也。陈氏曰。礼记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则其为虞官明矣。猎以虞为主。其实叹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与旧说不同。今存于此云云。按欧阳公作诗本义。常以序为證。而至此篇。独不取序说而据韩诗贾书之说。以明驺虞之为虞官。朱子于此亦存其说而不削。愚陋瞽见。或不至甚谬否。论语之书。各出于诸子之手。故记载之间。不能无可疑者。孔子称门人则必举其名例也。而称闵子骞之孝。不曰孝哉损也。如贤哉回也之例。下章侍侧。不称子骞。与下文子路子贡同例。胡氏以为闵氏门人所记者此也。然第十三篇冉子退朝。不称字。又何说以通之也。记门人之言则必称字。如仲弓问仁子路问政。子贡曰子夏曰之类是也。而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宰予昼寝。陈亢问于伯鱼。凡君问。称孔子对曰者。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4L 页
 尊君也。大夫之问。皆称子曰。如孟懿子,孟武伯之类是也。而至其答季康子之问。则除使民敬忠外。皆称孔子对曰。陈恒,崔抒弑君之贼也。书其弑君之恶。而或称谥或称子而不书名。是皆不能无疑也。季氏一篇。皆称孔子曰。阳货篇之子张问仁。尧曰篇之子张问政。非他弟子问仁问政之例。此又何说以通之也。尝窃伏思之。盖圣人之言语答问。德行仪容。当时门人在傍而详记之。又皆知足以知圣人而善观善言。故记录详尽。无复馀憾。至其裒集散稿。纂次成篇。则当时及门诸子。皆未及见。而成于诸子之门人后生也。是以容或有未尽契勘处。抑可见古人之质略。不似后世之弥文也。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以子称。洪氏以为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则孔子殁时。曾子之年。才二十七矣。曾子享年既久。卒传圣人之道。而此书记曾子启手足时语。则此书之成。在曾子既殁之后明矣。柳子厚所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者是也。而杨氏所谓各因其门人所记而失之不革者得之矣。
尊君也。大夫之问。皆称子曰。如孟懿子,孟武伯之类是也。而至其答季康子之问。则除使民敬忠外。皆称孔子对曰。陈恒,崔抒弑君之贼也。书其弑君之恶。而或称谥或称子而不书名。是皆不能无疑也。季氏一篇。皆称孔子曰。阳货篇之子张问仁。尧曰篇之子张问政。非他弟子问仁问政之例。此又何说以通之也。尝窃伏思之。盖圣人之言语答问。德行仪容。当时门人在傍而详记之。又皆知足以知圣人而善观善言。故记录详尽。无复馀憾。至其裒集散稿。纂次成篇。则当时及门诸子。皆未及见。而成于诸子之门人后生也。是以容或有未尽契勘处。抑可见古人之质略。不似后世之弥文也。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以子称。洪氏以为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则孔子殁时。曾子之年。才二十七矣。曾子享年既久。卒传圣人之道。而此书记曾子启手足时语。则此书之成。在曾子既殁之后明矣。柳子厚所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者是也。而杨氏所谓各因其门人所记而失之不革者得之矣。金泰叟尝言孟子万章篇首章父母之不我爱。于我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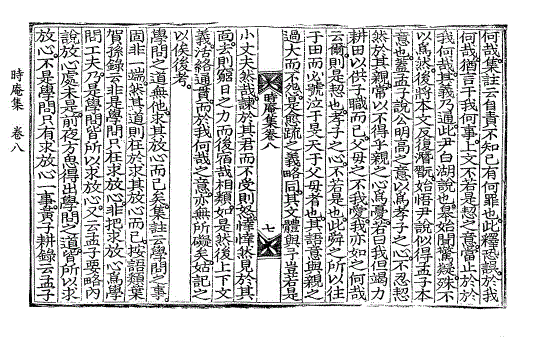 何哉。集注云自责不知己有何罪也。此释恐误。于我何哉。犹言干我何事。上文不若是恝之意。当止于于我何哉。其义乃通。此尹白湖说也。皋始闻惊疑。殊不以为然。后将本文反复潜玩。始悟尹说似得孟子本意也。盖孟子说公明高之意以为孝子之心。不忍恝然于其亲。常以不得乎亲之心为忧。若曰我但竭力耕田以供子职而已。父母之不我爱。我亦如之何哉云尔。则是恝也。孝子之心。不若是也。此舜之所以往于田而必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者也。其语意与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之义略同。其文体与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相类。如是然后上下文义。活络通贯。而于我何哉之意。亦无所碍矣。姑记之以俟后考。
何哉。集注云自责不知己有何罪也。此释恐误。于我何哉。犹言干我何事。上文不若是恝之意。当止于于我何哉。其义乃通。此尹白湖说也。皋始闻惊疑。殊不以为然。后将本文反复潜玩。始悟尹说似得孟子本意也。盖孟子说公明高之意以为孝子之心。不忍恝然于其亲。常以不得乎亲之心为忧。若曰我但竭力耕田以供子职而已。父母之不我爱。我亦如之何哉云尔。则是恝也。孝子之心。不若是也。此舜之所以往于田而必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者也。其语意与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之义略同。其文体与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相类。如是然后上下文义。活络通贯。而于我何哉之意。亦无所碍矣。姑记之以俟后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注云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按语类叶贺孙录云非是学问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为学问工夫。乃是学问皆所以求放心。又云孟子要略内说放心处未是。前夜方思得出学问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学问只有求放心一事。黄子耕录云孟子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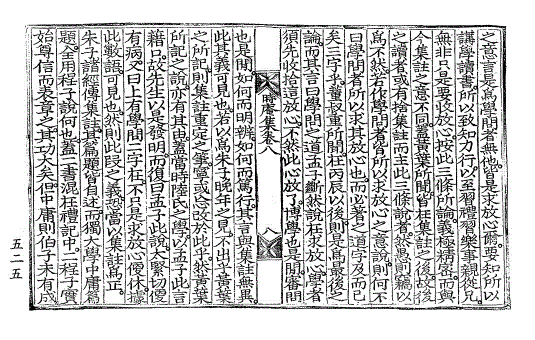 之意言是为学问者无他。皆是求放心尔。要知所以讲学读书。所以致知力行。以至习礼习乐事亲从兄。无非只是要收放心。按此三条所论。义极精密。而与今集注之意不同。盖黄叶所闻。皆在集注之后。故后之读者或有舍集注而主此三条说者。然愚则窃以为不然。若作学问者皆所以求放心之意说。则何不曰学问者所以求其放心也。而必著之道字及而已矣三字乎。董叔重所闻。在丙辰以后。则是为最后之论。而其言曰学问之道孟子断然说在求放心。学者须先收拾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学也是閒。审问也是閒。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笃行。其言与集注无异。此其义可见也。若以为朱子晚年之见。不出乎黄叶之所记。则集注重定之笔。宁或忘改于此乎。然黄叶所记之说。亦有其由。盖当时陆氏之学。以孟子此言藉口。故先生以是发明。而复曰孟子此说。太紧切便有病。又曰上有学问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据此数语。可见也。然则此段之义。恐当以集注为正。
之意言是为学问者无他。皆是求放心尔。要知所以讲学读书。所以致知力行。以至习礼习乐事亲从兄。无非只是要收放心。按此三条所论。义极精密。而与今集注之意不同。盖黄叶所闻。皆在集注之后。故后之读者或有舍集注而主此三条说者。然愚则窃以为不然。若作学问者皆所以求放心之意说。则何不曰学问者所以求其放心也。而必著之道字及而已矣三字乎。董叔重所闻。在丙辰以后。则是为最后之论。而其言曰学问之道孟子断然说在求放心。学者须先收拾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学也是閒。审问也是閒。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笃行。其言与集注无异。此其义可见也。若以为朱子晚年之见。不出乎黄叶之所记。则集注重定之笔。宁或忘改于此乎。然黄叶所记之说。亦有其由。盖当时陆氏之学。以孟子此言藉口。故先生以是发明。而复曰孟子此说。太紧切便有病。又曰上有学问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据此数语。可见也。然则此段之义。恐当以集注为正。朱子诸经传集注。其篇题皆自述。而独大学中庸篇题。全用程子说何也。盖二书混在礼记中。二程子实始尊信而表章之。其功大矣。但中庸则伯子未有成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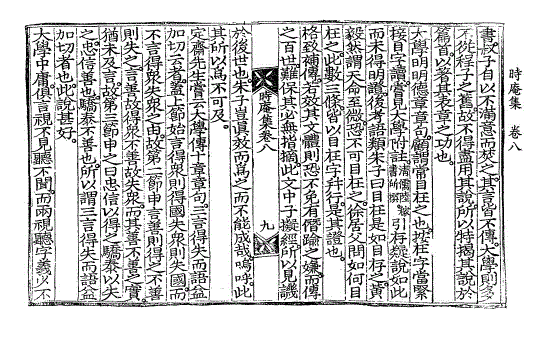 书。叔子自以不满意而焚之。其言皆不传。大学则多不从程子之旧。故不得尽用其说。所以特揭其说于篇首。以著其表章之功也。
书。叔子自以不满意而焚之。其言皆不传。大学则多不从程子之旧。故不得尽用其说。所以特揭其说于篇首。以著其表章之功也。大学明明德章章句。顾谓常目在之也。按在字当紧接目字读。尝见大学附注。(清儒陆稼书所撰。)引存疑说如此而未得明證。后考语类朱子曰目在是如目存之。黄毅然谓天命至微。恐不可目在之。徐居父问如何目在之。此数三条。皆以目在字并行。是其證也。
格致补传。若效其文体则恐不免有僭踰之嫌。而传之百世。难保其必无指摘。此文中子拟经。所以见讥于后世也。朱子岂真效而为之而不能成哉。呜呼。此其所以为不可及。
定斋先生尝云大学传十章章句。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云者。盖上节始言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而不言得众失众之由。故第二节申言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言善故得众不善故失众。而其善不善之实。犹未及言。故第三节申之曰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忠信善也。骄泰不善也。所以谓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者也。此说甚好。
大学中庸。俱言视不见听不闻。而两视听字义少不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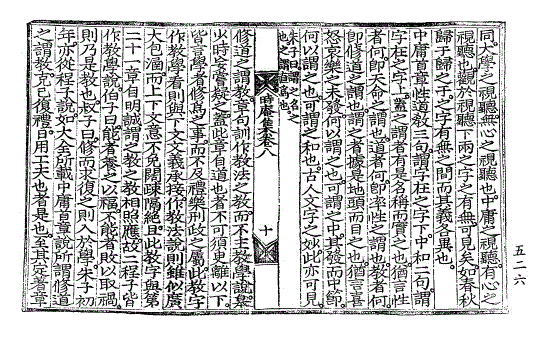 同。大学之视听。无心之视听也。中庸之视听。有心之视听也。观于视听下两之字之有无。可见矣。如春秋归于归之于。之字有无之间而其义各异也。
同。大学之视听。无心之视听也。中庸之视听。有心之视听也。观于视听下两之字之有无。可见矣。如春秋归于归之于。之字有无之间而其义各异也。中庸首章性道教三句。谓字在之字下。中和二句。谓字在之字上。盖之谓者有是名称而实之也。犹言性者何。即天命之谓也。道者何。即率性之谓也。教者何。即修道之谓也。谓之者据是地头而目之也。犹言喜怒哀乐之未发。何以谓之也。可谓之中。其发而中节。何以谓之也。可谓之和也。古人文字之妙。此亦可见。(朱子曰。谓之名之也。之谓直为也。)
修道之谓教。章句训作教法之教。而不主教学说。皋少时妄尝疑之。盖此章自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以下。皆言学者修为之事。而不及礼乐刑政之属。此教字作教学看则与下文文义承接。作教法说则虽似广大包涵。而上下文意不免阔疏隔绝。且此教字与第二十一章自明诚谓之教之教相照应。故二程子皆作教学说。伯子曰。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则乃是教也。叔子曰。修而求复之则入于学。朱子初年。亦从程子说。如大全所载中庸首章说所谓修道之谓教。克己复礼。日用工夫也者是也。至其定著章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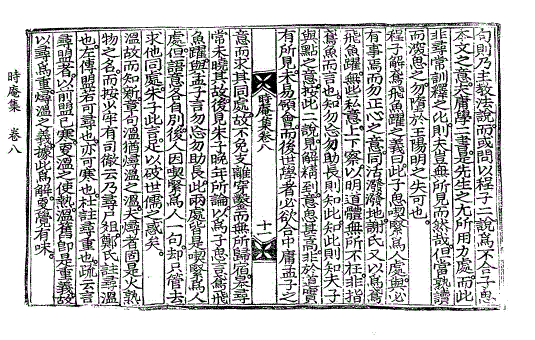 句则乃主教法说。而或问以程子二说为不合子思本文之意。夫庸学二书。是先生之尤所用力处。而此非寻常训释之比。则夫岂无所见而然哉。但当熟读而深思之。勿堕于王阳明之失可也。
句则乃主教法说。而或问以程子二说为不合子思本文之意。夫庸学二书。是先生之尤所用力处。而此非寻常训释之比。则夫岂无所见而然哉。但当熟读而深思之。勿堕于王阳明之失可也。程子解鸢飞鱼跃之义曰。此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谢氏又以为鸢飞鱼跃。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按此二说。见解精到。意思甚高。非于道实有所见。未易领会。而后世学者必欲合中庸孟子之意而求其同处。故不免支离穿凿而无所归宿。皋寻常未晓其故。后见朱子晚年所论。以为子思言鸢飞鱼跃。与孟子言勿忘勿助长。此两处皆是吃紧为人处。但语意各自别。后人因吃紧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处。朱子此言。足以破世儒之惑矣。
温故而知新。章句温犹燖温之温。夫燖者固是火熟物之名。而按少牢有司彻云乃寻尸俎。郑氏注寻温也。左传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杜注寻重也。疏云言寻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热。温旧即是重义。故以寻为重。燖温之义。据此为解。更觉有味。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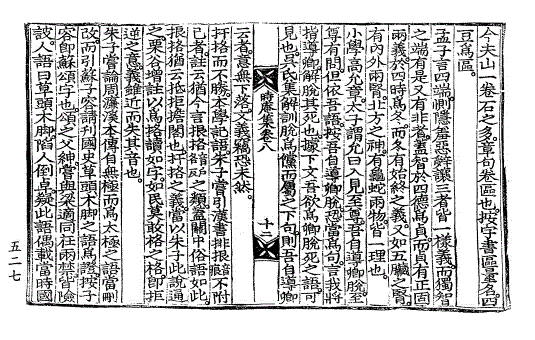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章句卷区也。按字书区量名。四豆为区。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章句卷区也。按字书区量名。四豆为区。孟子言四端。恻隐羞恶辞让三者皆一样义。而独智之端有是又有非者。盖智于四德为贞。而贞有正固两义。于四时为冬。而冬有始终之义。又如五脏之肾。有内外两肾。北方之神。有龟蛇两物。皆一理也。
小学高允章。太子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按吾自导卿脱。恐当为句。言我将指导卿。解脱其死也。据下文吾欲为卿脱死之语。可见也。吴氏集解训脱为傥而属之下句。则吾自导卿云者。意无下落。文义窃恐未然。
捍格而不胜。本学记语。朱子尝引汉书排拫(音痕)不附己者。注云犹今言拫格(音户各反)之类。盖关中俗语如此。拫格犹云抵拒担阁也。捍格之义。当以朱子此说通之。栗谷增注以为格读如字。如民莫敢格之格。即拒逆之意。义虽近而失其音也。
朱子尝论周濂溪本传自无极而为太极之语当删改。而引苏子容请刊国史草头木脚之语为證。按子容即苏颂字也。颂之父绅。尝与梁适同在两禁。皆险诐。人语曰草头木脚。陷人倒卓。疑此语偶载当时国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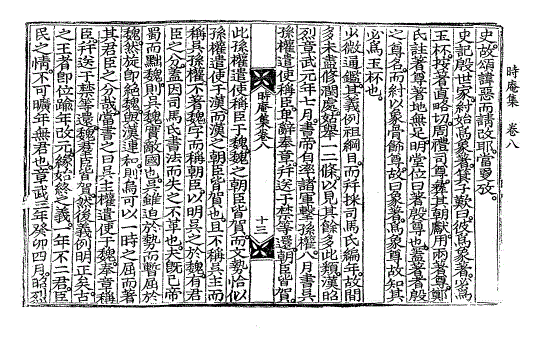 史。故颂讳恶而请改耶。当更考。
史。故颂讳恶而请改耶。当更考。史记殷世家。纣始为象著。箕子叹曰。彼为象著。必为玉杯。按著直略切。周礼司尊。彝其朝献。用两著尊。郑氏注著尊著地无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盖著者殷之尊名。而纣以象骨饰尊。故曰象著。为象尊故知其必为玉杯也。
少微通鉴。其义例祖纲目。而并采司马氏编年。故间多未尽修润处。姑举一二条。以见其馀多此类。汉昭烈章武元年七月。书帝自率诸军击孙权。八月书吴孙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朝臣皆贺。此孙权遣使称臣于魏。魏之朝臣皆贺。而文势恰似孙权遣使于汉。而汉之朝臣皆贺也。且不称吴主而称吴孙权。不著魏字而称朝臣。以明吴之于魏。有君臣之分。盖因司马氏书法而失之不革也。夫既已帝蜀而黜魏。则吴魏实敌国也。吴虽迫于势而暂屈于魏。然旋即绝魏。与汉连和。则乌可以一时之屈而著其君臣之分哉。当书之曰吴主权遣使于魏。奉章称臣。并送于禁等还。魏群臣皆贺。然后义例明正矣。古之王者即位踰年改元。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臣民之情。不可旷年无君也。章武三年癸卯四月。昭烈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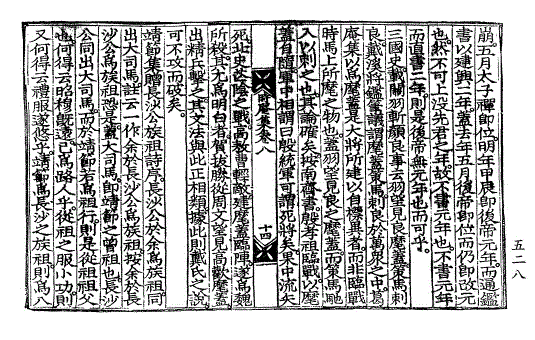 崩。五月太子禅即位。明年甲辰即后帝元年。而通鉴书以建兴二年。盖去年五月后帝即位而仍即改元也。然不可上没先君之年。故不书元年也。不书元年而直书二年。则是后帝无元年也而可乎。
崩。五月太子禅即位。明年甲辰即后帝元年。而通鉴书以建兴二年。盖去年五月后帝即位而仍即改元也。然不可上没先君之年。故不书元年也。不书元年而直书二年。则是后帝无元年也而可乎。三国史。载关羽斩颜良事云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戴溪将鉴笔议谓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葛庵集以为麾盖是大将所建以自标异者。而非临战时马上所麾之物也。盖羽望见良之麾盖。而策马驰入以刺之也。其论确矣。按南齐书。殷孝祖临战。以麾盖自随。军中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将矣。果中流矢死。北史芒阴之战。高敖曹轻敌。建麾盖临阵。遂为魏所杀。其尤为明白者。贺拔胜从周文望见高欢麾盖。出精兵击之。其文法与此正相类。据此则戴氏之说。可不攻而破矣。
靖节集赠长沙公族祖诗序。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注云一作余于长沙公为族祖。按余于长沙公为族祖恐是。盖大司马。即靖节之曾祖也。长沙公同出大司马。而于靖节若为祖行。则是从祖祖父也。何得云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乎。从祖之服小功。则又何得云礼服遂悠乎。靖节为长沙之族祖。则为八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9H 页
 寸族祖而服尽矣。故曰昭穆既远。礼服遂悠也。然则赠长沙公族祖之祖恐作孙。于理为顺。
寸族祖而服尽矣。故曰昭穆既远。礼服遂悠也。然则赠长沙公族祖之祖恐作孙。于理为顺。余少时观程氏外书。有敬下驴不起五字。而其下注云陈先生大分守不足。未晓其义。后见陈后山骑驴诗。复作骑驴不下驴。注禅林中谓参禅人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二是骑却驴不肯下。识得驴了。骑却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难医。若解放下。方唤作无事道人。盖程子尝论敬引禅家此语。而记者失之略耳。所云陈先生。恐或指后山而言耶。
朱子大全跋王枢密答司马忠洁公帖。谨考跋语。乃忠洁公滞北虏时报答王枢密书。而非枢密答忠洁公书也。书中有陈谢上赐之语。故枢密缴进于上也。不然跋文何以曰此其报王枢密手书。而王公缴进之章也。跋题恐当作司马忠洁公答王枢密帖。
张无垢中庸解云未发以前。戒慎恐惧。无一毫私欲。朱子辨之曰。未发以前。天理浑然。戒慎恐惧则既发矣。按此以戒慎恐惧为既发。与章句或问不同。可疑也。盖杂学辨中所论。与今集注诸书或有不同处。何叔京跋文。在乾道丙戌。则此辨之作。是先生三十六七岁时事。容有未尽契勘。恐当以集注章句为正。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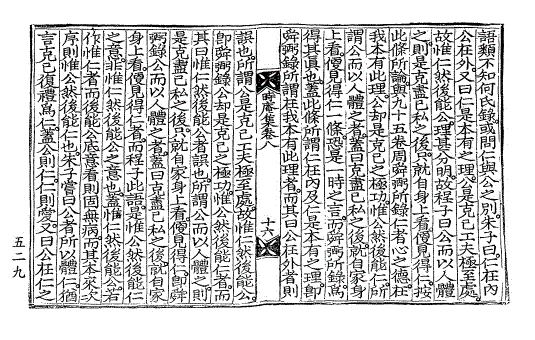 语类不知何氏录。或问仁与公之别。朱子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按此条所论。与九十五卷周舜弼所录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却是克己之极功。惟公然后能仁。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者。盖曰克尽己私之后。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一条。恐是一时之言。而舜弼所录。为得其真也。盖此条所谓仁在内及仁是本有之理。即舜弼录所谓在我本有此理者。而其曰公在外者则误也。所谓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即舜弼录公却是克己之极功。惟公然后能仁者。而其曰惟仁然后能公者误也。所谓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即舜弼录公而以人体之者。盖曰克尽己私之后。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者。而程子此语。是惟公然后能仁之意。非惟仁然后能公之意也。盖惟仁然后能公。若作惟仁者而后能公底意看则固无病。而其本来次序则惟公然后能仁也。朱子尝曰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盖公则仁。仁则爱。又曰公在仁之
语类不知何氏录。或问仁与公之别。朱子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按此条所论。与九十五卷周舜弼所录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却是克己之极功。惟公然后能仁。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者。盖曰克尽己私之后。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一条。恐是一时之言。而舜弼所录。为得其真也。盖此条所谓仁在内及仁是本有之理。即舜弼录所谓在我本有此理者。而其曰公在外者则误也。所谓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即舜弼录公却是克己之极功。惟公然后能仁者。而其曰惟仁然后能公者误也。所谓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即舜弼录公而以人体之者。盖曰克尽己私之后。就自家身上看。便见得仁者。而程子此语。是惟公然后能仁之意。非惟仁然后能公之意也。盖惟仁然后能公。若作惟仁者而后能公底意看则固无病。而其本来次序则惟公然后能仁也。朱子尝曰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盖公则仁。仁则爱。又曰公在仁之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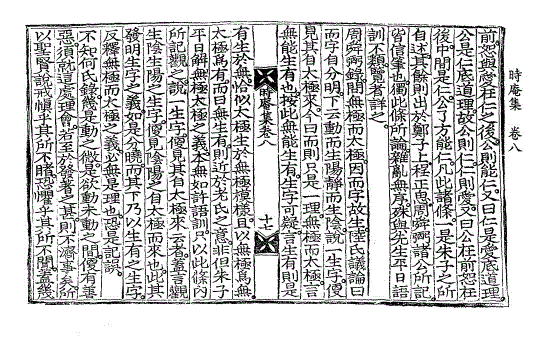 前。恕与爱在仁之后。公则能仁。又曰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又曰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凡此诸条。一是朱子之所自述。其馀则出于郑子上,程正思,周舜弼诸公所记。皆信笔也。独此条所论。杂乱无序。殊与先生平日语训不类。览者详之。
前。恕与爱在仁之后。公则能仁。又曰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又曰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凡此诸条。一是朱子之所自述。其馀则出于郑子上,程正思,周舜弼诸公所记。皆信笔也。独此条所论。杂乱无序。殊与先生平日语训不类。览者详之。周舜弼录。问无极而太极。因而字故生。陆氏议论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说一生字。便见其自太极来。今曰而则只是一理。无极而太极。言无能生有也。按此无能生有。生字可疑。言生有则是有生于无。恰似太极生于无极模样。且以无极为无。太极为有。而曰无生有。则近于老氏之意。非但朱子平日解无极太极之义。本无如许语训。只以此条内所记观之。说一生字。便见其自太极来云者。盖言观生阴生阳之生字。便见阴阳之自太极而来也。此其发明生字之义。如是分晓。而其下乃以生有之生字。反释无极而太极之义。必无是理也。恐是记误。
不知何氏录。几是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须就这处理会。若至于发著之甚。则不济事矣。所以圣贤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几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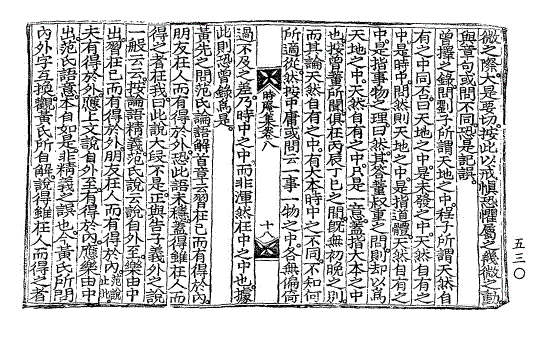 微之际。大是要切。按此以戒慎恐惧属之几微之动。与章句或问不同。恐是记误。
微之际。大是要切。按此以戒慎恐惧属之几微之动。与章句或问不同。恐是记误。曾择之录。问刘子所谓天地之中。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发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时中。问然则天地之中。是指道体。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其答董叔重之问。则却以为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只是一意。盖指大本之中也。按曾董所闻。俱在丙辰丁巳之间。既无初晚之别。而其论天然自有之中。有大本时中之不同。不知何所适从。然按中庸或问云一事一物之中。各无偏倚过不及之差。乃时中之中。而非浑然在中之中也。据此则恐曾录为是。
黄先之问范氏论语解首章云习在己而有得于内。朋友在人而有得于外。恐此语未稳。盖得虽在人而得之者在我。曰此说大段不是。正与告子义外之说一般云云。按论语精义。范氏说云说自外至。乐由中出。习在己而有得于外。朋友在人而有得于内。(范说止此。)夫有得于外。应上文说自外至。有得于内。应乐由中出。范氏语意。本自如是。非精义之误也。今黄氏所问内外字互换。观黄氏所自解。说得虽在人而得之者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1H 页
 在我之云。正驳朋友在人而有得于外之意。则亦非语类之误也。窃尝思之。盖黄氏举范说为问而失于捡点。致有内外字之互换。然无论在己在人。但曰得于外则便堕义外之失。故朱子答其大意而未暇订正其误字也耶。
在我之云。正驳朋友在人而有得于外之意。则亦非语类之误也。窃尝思之。盖黄氏举范说为问而失于捡点。致有内外字之互换。然无论在己在人。但曰得于外则便堕义外之失。故朱子答其大意而未暇订正其误字也耶。王幼观录。学而时习之。或问云学是未知而求知底工夫。习是未能而求能底工夫。按今论语或问中无此语。有曰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学之事也。既学而知且能矣。而于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时反复而温绎之云云。与此条学为知习为行之说。辞旨不同。王氏所问。恐是或问之初本也欤。
先生顾陈安卿曰。伊川谓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实理与实见不同。盖有那实理。人须是实见得。今合说。必记录有误。按朱子既以程子此语为记误。而论语集注引用何也。盖理自是理。见自是见。而今以实理为实见得。虽似少欠段落。而全篇语意。确实痛切。其发明杀身成仁之义。极为有力于学者。故载之。先生尝谓伊川云心生道也。此句是张思叔所记。疑有欠阙处。吴伯丰云何故入在近思录中。曰如何敢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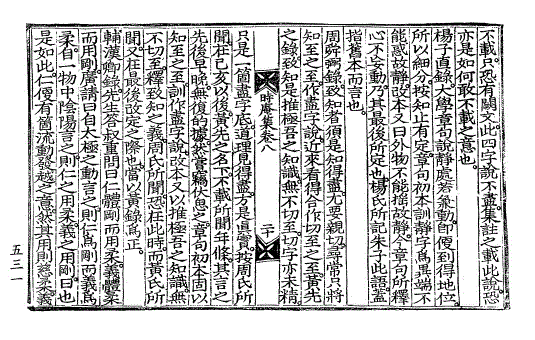 不载。只恐有阙文。此四字说不尽。集注之载此说。恐亦是如何敢不载之意也。
不载。只恐有阙文。此四字说不尽。集注之载此说。恐亦是如何敢不载之意也。杨子直录。大学章句说静处若兼动。即便到得地位。所以细分。按知止有定。章句初本训静字为异端不能惑故静。改本又曰外物不能摇故静。今章句所释心不妄动。乃其最后所定也。杨氏所记朱子此语。盖指旧本而言也。
周舜弼录。致知者须是知得尽。尤要亲切。寻常只将知至之至。作尽字说。近来看得合作切至之至。黄先之录。致知是推极吾之知识。无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个尽字底。道理见得尽。方是真实。按周氏所闻。在己亥以后。黄先之名下。不载所闻年条。其言之先后早晚。无复的据。然尝窃伏思之。章句初本固以知至之至。训作尽字说。改本又以推极吾之知识。无不切至。释致知之义。周氏所闻。恐在此时。而黄氏所闻。又在最后改定之际也。当以黄录为正。
辅汉卿录。先生答叔重问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广请曰自太极之动言之。则仁为刚而义为柔。自一物中阴阳言之。则仁之用柔。义之用刚。曰也是如此。仁便有个流动发越之意。然其用则慈柔。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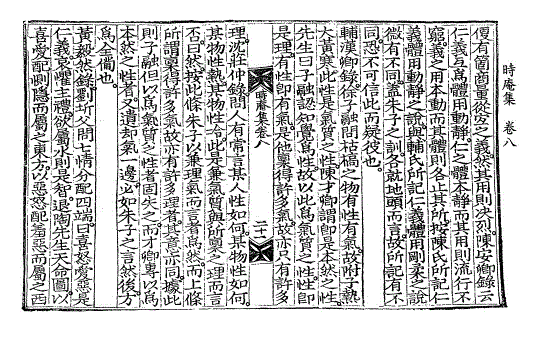 便有个商量从宜之义。然其用则决烈。陈安卿录云仁义互为体用动静。仁之体本静而其用则流行不穷。义之用本动而其体则各止其所。按陈氏所记仁义体用动静之说。与辅氏所记仁义体用刚柔之说微有不同。盖朱子之训。各就地头而言。故所记有不同。恐不可信此而疑彼也。
便有个商量从宜之义。然其用则决烈。陈安卿录云仁义互为体用动静。仁之体本静而其用则流行不穷。义之用本动而其体则各止其所。按陈氏所记仁义体用动静之说。与辅氏所记仁义体用刚柔之说微有不同。盖朱子之训。各就地头而言。故所记有不同。恐不可信此而疑彼也。辅汉卿录。徐子融问枯槁之物有性有气。故附子热大黄寒。此性是气质之性。陈才卿谓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认知觉为性。故以此为气质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气。是他禀得许多气。故亦只有许多理。沈庄仲录。问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热。某物性冷。此是兼气质与所禀之理而言否。曰然。按此条朱子以兼理气而言者为然。而上条所谓禀得许多气故亦有许多理者。其意亦同。据此则子融但以为气质之性者固失之。而才卿专以为本然之性者。又遗却气一边。必如朱子之言然后。方为全备也。
黄毅然录。刘圻父问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爱恶是仁义。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退陶先生天命图。以喜爱配恻隐而属之东方。以恶怒配羞恶而属之西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2L 页
 方。以哀乐配辞让而属之南方。以欲配是非而属之北方。盖主此说。而欲字之斜在东北间者。又据朱子爱与欲相似之说也。然不知何氏录。却以喜属火。哀惧亦属水。叶味道录。又以为哀惧只是从恻隐发。则又以哀与惧属之木也。三条所记。
方。以哀乐配辞让而属之南方。以欲配是非而属之北方。盖主此说。而欲字之斜在东北间者。又据朱子爱与欲相似之说也。然不知何氏录。却以喜属火。哀惧亦属水。叶味道录。又以为哀惧只是从恻隐发。则又以哀与惧属之木也。三条所记。或问向蒙见教。读书须要涵泳。须要浃洽。因看孟子。千言万语。只是论心。七篇之书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又一人云先生涵泳之说。乃杜元凯优而柔之之意。朱子曰。某为见此中人读书。大段卤莽。所以说读书。须当涵泳。所谓涵泳者。只是子细读书之异名也。按此所云涵泳。与程子说涵养。其字义意思迥然相别。而后之学者不察。或误以涵泳作涵养则大误。涵养岂子细读书之异名耶。
论礼让为国章。先生叹息言古人禁人聚敛。今却张官置吏。惟恐人不来敛。考异云敛一误饮。按饮字为是。此盖朱子叹当时榷酒之弊也。榷酤之法。官置榷场以卖酒。民有欲饮者皆来沽官酒。此朱子所以叹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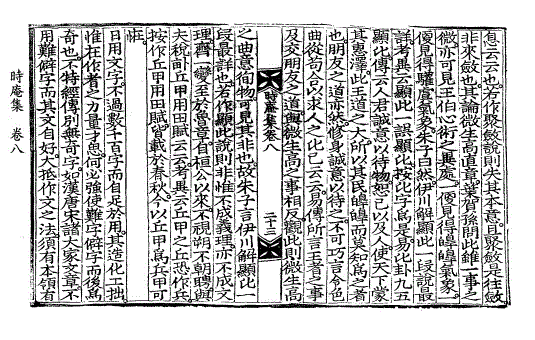 息云云也。若作聚敛说则失其本意。且聚敛是往敛。非来敛也。其论微生高直章。叶贺孙问此虽一事之微。亦可见王伯心术之异处。一便见得皞皞气象。一便见得驩虞气象。朱子曰然。伊川解显此一段说最详。考异云显此一误显比。按比字为是。易比卦九五显比。传云人君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使天下蒙其惠泽。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朋友之道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云云。易传所言王者之事及交朋友之道。与微生高之事相反。观此则微生高之曲意徇物。可见其非也。故朱子言伊川解显比一段最详也。若作显此说则非惟不成义理。亦不成文理。齐一变至于鲁章。自桓公以来。不视朔不朝聘。与夫税亩丘甲用田赋云云。考异云丘甲之丘恐作兵。按作丘甲用田赋。皆载于春秋。今以丘甲为兵甲可怪。
息云云也。若作聚敛说则失其本意。且聚敛是往敛。非来敛也。其论微生高直章。叶贺孙问此虽一事之微。亦可见王伯心术之异处。一便见得皞皞气象。一便见得驩虞气象。朱子曰然。伊川解显此一段说最详。考异云显此一误显比。按比字为是。易比卦九五显比。传云人君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使天下蒙其惠泽。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朋友之道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云云。易传所言王者之事及交朋友之道。与微生高之事相反。观此则微生高之曲意徇物。可见其非也。故朱子言伊川解显比一段最详也。若作显此说则非惟不成义理。亦不成文理。齐一变至于鲁章。自桓公以来。不视朔不朝聘。与夫税亩丘甲用田赋云云。考异云丘甲之丘恐作兵。按作丘甲用田赋。皆载于春秋。今以丘甲为兵甲可怪。日用文字。不过数千百字而自足于用。其造化工拙。惟在作者之力量才思。何必强使难字僻字而后为奇也。不特经传别无奇字。如汉唐宋诸大家文章。不用难僻字而其文自好。大抵作文之法。须有本领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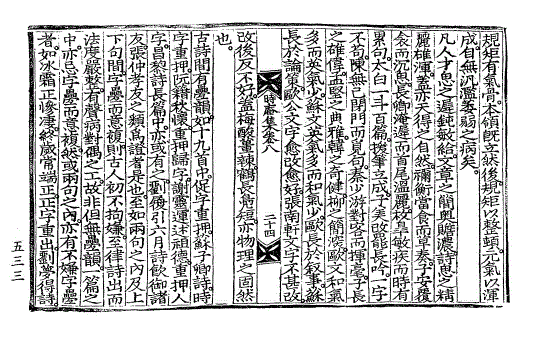 规矩有气骨。本领既立然后。规矩以整顿。元气以浑成。自无汎滥萎弱之病矣。
规矩有气骨。本领既立然后。规矩以整顿。元气以浑成。自无汎滥萎弱之病矣。凡人才思之迟钝敏给。文章之𥳑奥赡浓。诗思之精丽雄浑。盖亦天得之自然。祢衡当食而草奏。子安覆衾而沉思。长卿淹迟而首尾温丽。枚皋敏疾而时有累句。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陈无己闭门而觅句。秦少游对客而挥毫。子长之雄伟。孟坚之典雅。韩之奇健。柳之简深。欧文和气多而英气少。苏文英气多而和气少。欧长于叙事。苏长于论策。欧公文字愈改愈好。张南轩文字不甚改。改后反不好。盖梅酸姜辣。鹤长凫短。亦物理之固然也。
古诗间有叠韵。如十九首中。促字重押。苏子卿诗。时字重押。阮籍秋怀。重押归字。谢灵运述祖德。重押人字。昌黎诗长篇中。亦或有之。刘履引六月诗饮御诸友。张仲孝友之类为證者是也。至如两句之内及上下句间。字叠而意复。则古人初不拘嫌。至律诗出而法度严整。有声病对偶之工。故非但无叠韵。一篇之中。亦忌字叠而意复。然或两句之内。亦有不嫌字叠者。如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正字重出。刘梦得诗。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4H 页
 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相字重出。吕与叔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如字重出。朱晦翁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人字重出。欧阳公诗。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两为字相对。苏东坡诗。白发怜君略相似。青山许我定相从。两相字相对而亦不嫌。我东诗人闻见不广。无论两句之内。不得用叠字。即一篇之中。偶有叠字。则不惟傍观之窃笑。己亦以为病。必改使他字而后。慊于心而免人之讥贬。其弊至此。而诗之本义。几乎息矣。可叹。
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相字重出。吕与叔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殆类俳。如字重出。朱晦翁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人字重出。欧阳公诗。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两为字相对。苏东坡诗。白发怜君略相似。青山许我定相从。两相字相对而亦不嫌。我东诗人闻见不广。无论两句之内。不得用叠字。即一篇之中。偶有叠字。则不惟傍观之窃笑。己亦以为病。必改使他字而后。慊于心而免人之讥贬。其弊至此。而诗之本义。几乎息矣。可叹。古今论诗者。必以杜子美为称首。余少时却喜李白诗而不甚喜杜诗。自以为眼目不到故如是。后见欧苏诸公皆以杜诗为有俗气。朱子亦曰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诗都不可晓。又曰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杜晚年诗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又尝谓太白诗。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又曰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夫以欧苏之文章识见而其言如此。朱子之于李杜。亦微有低仰之权衡。夫岂无所见而然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4L 页
 三百篇后。诗至杜子美而众体毕备。先秦以后。文至韩昌黎而众体毕备。自二子以来数千年间。以诗文名世者。不翅千百家。而皆不能出乎二子范围之内。由是观之。二子乃千古诗文之宗匠也。
三百篇后。诗至杜子美而众体毕备。先秦以后。文至韩昌黎而众体毕备。自二子以来数千年间。以诗文名世者。不翅千百家。而皆不能出乎二子范围之内。由是观之。二子乃千古诗文之宗匠也。朱子以举子程文。为人之一厄。谓人过了此一厄。当理会学问。噫。今人何止是一厄。平生都是这个厄。虽有才高质美。可以有为之人。只恁地汩没滚倒。出脱不得这个厄。毕竟虚送了一生。可叹。
书疏者。所以道情素通慇勤也。与人书疏。当致其谨审谦恭。盖道理当然。而荣辱祸福。亦未尝不由之。昔席豫与子弟书。不作草字。其谨慎可法也。何绥(曾之孙)与人书疏。辞礼简傲。王尼见绥书。谓人曰伯蔚(绥之字)居乱世而矜豪。乃尔其能免乎。后果为太傅越所杀。夫绥之平日汰侈。固足以杀身湛宗。不止书疏之简傲而已。然此亦其取祸之一段也。
范至能跋司马温公帖云世传字书似其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献之严整而好作草书。王文正之沉毅而笔意洒落。攲侧有态。岂皆似其人哉。惟温公则几耳。开卷俨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尽。黄山谷亦云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5H 页
 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朱子跋韩魏公帖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许忙事。此虽戏言。实中其病。某平日得见韩魏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皆端严谨重。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签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皋性不便书。知旧书疏。例皆倩手。或不得而自为之则失于敬谨。丑拙可笑。每诵诸先辈之说。未尝不愧惧也。
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朱子跋韩魏公帖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许忙事。此虽戏言。实中其病。某平日得见韩魏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皆端严谨重。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签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皋性不便书。知旧书疏。例皆倩手。或不得而自为之则失于敬谨。丑拙可笑。每诵诸先辈之说。未尝不愧惧也。胡文定撰杨龟山墓志。有曰公知时势将变。又曰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又举龟山陈戒中酌中立额之语。直书龟山之名与字而不以为嫌。盖偏名不讳。而表德则元无讳之之法。不特此志为然。古人文字。槩多有此例。此古人质实处也。
朱子称程子谓子程子。陈定宇云上子字后学宗师先儒之称。此说是矣而犹未尽。盖孔门弟子称孔子。专称曰子。后世因孔门有专称为子之例。于是有以子为师之专称者。公羊传有子沈子,子司马子。何休释曰加子于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也。梁溪漫志云列子书。亦其门人所集。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5L 页
 故曰子列子。子冠氏上。明其为师也。不但言子者所以避孔子也。据此数说则朱子之称子程子。盖亦自托于弟子之列也。大学序私淑二字。可见其本意也。
故曰子列子。子冠氏上。明其为师也。不但言子者所以避孔子也。据此数说则朱子之称子程子。盖亦自托于弟子之列也。大学序私淑二字。可见其本意也。陈清澜学蔀通辨云近世宗尚陆学者。皆自幼从朱子之教。读圣贤之书。理颇明矣。然后厌浅近而好高奇。厌繁难而趋简径。其议道述言。高谈阔论。虽曰宗陆。而实朱子之教。有以启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即从象山之教。而捐书绝学。遗物弃事。屏思黜虑。专一澄心。不以言语文字为意。不恤视听言动非礼。不知成甚么人。陈氏之言。可谓陆学者顶门上一针。续编上卷。引朱子读大纪说。有未尽删节处。幸而有一间世之杰乃能不为之屈而有声罪致讨之心焉此二十三字恐当删。
客有论丙子事者曰。当时若不为城下之盟。 宗社不得保。夫我国之于大明。虽有君臣之名。不过海外之一藩邦也。为明而亡我世守之宗社可乎哉。由是言之。崔相国存社之功。岂不优于三学士殉义乎。余曰。若客之言。是徒知有利而已。不知有仁义也。夫我国之服事大明。自 太祖建国时。受命于高皇帝。而列圣朝殊恩异渥。有内服臣子之所不能得者。及壬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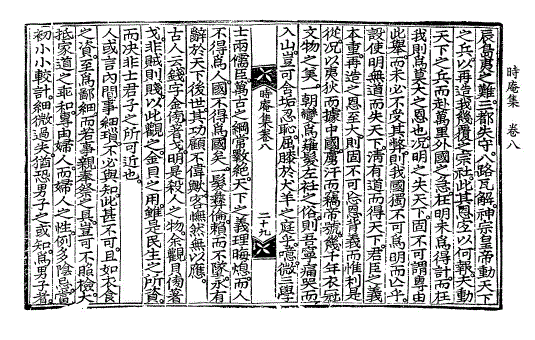 辰岛夷之难。三都失守。八路瓦解。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以再造我几覆之宗社。此其恩宜以何报。夫动天下之兵而赴万里外国之急。在明未为得计。而在我则为莫大之恩也。况明之失天下。固不可谓专由此举。而未必不受其弊。则我国独不可为明而亡乎。设使明无道而失天下。清有道而得天下。君臣之义本重。再造之恩至大。则固不可忘恩背义而惟利是从。况以夷狄而据中国。虏汗而窃帝号。几千年衣冠文物之美。一朝变为薙发左衽之俗。则吾宁痛哭而入山。岂可含垢忍耻。屈膝于犬羊之庭乎。噫。微三学士两儒臣。万古之纲常斁绝。天下之义理晦熄。而人不得为人。国不得为国矣。一发彝伦。赖而不坠。永有辞于天下后世。其功顾不伟欤。客怃然无以应。
辰岛夷之难。三都失守。八路瓦解。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以再造我几覆之宗社。此其恩宜以何报。夫动天下之兵而赴万里外国之急。在明未为得计。而在我则为莫大之恩也。况明之失天下。固不可谓专由此举。而未必不受其弊。则我国独不可为明而亡乎。设使明无道而失天下。清有道而得天下。君臣之义本重。再造之恩至大。则固不可忘恩背义而惟利是从。况以夷狄而据中国。虏汗而窃帝号。几千年衣冠文物之美。一朝变为薙发左衽之俗。则吾宁痛哭而入山。岂可含垢忍耻。屈膝于犬羊之庭乎。噫。微三学士两儒臣。万古之纲常斁绝。天下之义理晦熄。而人不得为人。国不得为国矣。一发彝伦。赖而不坠。永有辞于天下后世。其功顾不伟欤。客怃然无以应。古人云钱字金傍著戈。明是杀人之物。余观贝傍著戈。非贼则贱。以此观之。金贝之用。虽是民生之所资。而决非士君子之所可近也。
人或言内间事细琐。不必与知。此甚不可。且如衣食之资。至为鄙细。而若事亲奉祭之具。岂可不照检。大抵家道之乖和。专由妇人。而妇人之性。例多阴忌。当初小小较计。细微过失。犹恐男子之或知。为男子者。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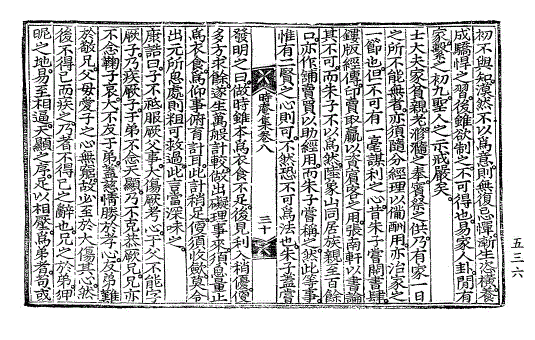 初不与知。漠然不以为意。则无复忌惮。渐生恣横。养成骄悍之习。后虽欲制之。不可得也。易家人卦。閒有家。系之初九。圣人之示戒严矣。
初不与知。漠然不以为意。则无复忌惮。渐生恣横。养成骄悍之习。后虽欲制之。不可得也。易家人卦。閒有家。系之初九。圣人之示戒严矣。士大夫家贫亲老。𣺫瀡之奉。宾祭之供。乃有家一日之所不能无者。亦须随分经理以备酬用。亦治家之一节也。但不可有一毫谋利之心。昔朱子尝开书肆。镂版经传。印卖取赢以资宾客之用。张南轩以书论其不可。而朱子不以为然。陆象山同居族亲至百馀口。亦作铺卖买以助经用。而朱子尝称之。然此等事。惟有二贤之心则可。不然恐不可为法也。朱子盖尝发明之曰。做时虽本为衣食不足。后见利入稍优。便多方求馀。遂生万般计较。做出碍理事来。须思量止为衣食。为仰事俯育计耳。此计稍足。便须收敛。莫令出元所思处则粗可救过。此言当深味之。
康诰曰。子不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不念天显。乃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盖慈情胜于孝心。友弟难于敬兄。父母爱子之心无穷。故必至于大伤其心。然后不得已而疾之。乃者不得已之辞也。兄之于弟。狎昵之地。易至相逼。天显之序。足以相压。为弟者。苟或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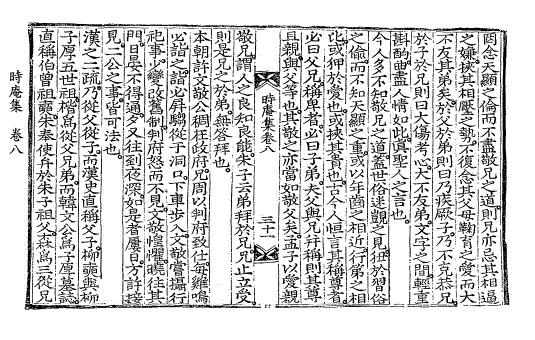 罔念天显之伦而不尽敬兄之道。则兄亦忌其相逼之嫌。挟其相压之势。不复念其父母鞠育之爱而大不友其弟矣。于父于弟则曰乃疾厥子。乃不克恭兄。于子于兄则曰大伤考心。大不友弟。文字之间。轻重斟酌。曲尽人情如此。真圣人之言也。
罔念天显之伦而不尽敬兄之道。则兄亦忌其相逼之嫌。挟其相压之势。不复念其父母鞠育之爱而大不友其弟矣。于父于弟则曰乃疾厥子。乃不克恭兄。于子于兄则曰大伤考心。大不友弟。文字之间。轻重斟酌。曲尽人情如此。真圣人之言也。今人多不知敬兄之道。盖世俗迷觊之见。狃于习俗之偷。而不知天显之重。或以年齿之相近。行第之相比。或狎于爱也。或挟其贵也。古今人恒言其称尊者。必曰父兄。称卑者。必曰子弟。夫父与兄并称则其尊且亲。与父等也。其敬之亦当如敬父矣。孟子以爱亲敬兄。谓人之良知良能。朱子云弟拜于兄。兄止立受。则是兄之于弟。无答拜也。
本朝许文敬公稠在政府。兄周以判府致仕。每鸡鸣必诣之。诣必屏驺从于洞口。下车步入。文敬尝摄行祀事。少变改旧制。判府怒而不见。文敬惶惧。晓往其门。日晏不得通。夕又往到夜深。如是者屡日。方许接见。二公之事。皆可法也。
汉之二疏。乃从父从子。而汉史直称父子。柳奭与柳子厚五世祖。楷为从父兄弟。而韩文公为子厚墓志。直称伯曾祖奭。朱奉使弁于朱子祖父。森为三从兄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7L 页
 弟。而朱子撰其行状及祭文。皆称叔祖。自称从孙。程允夫为韦斋内弟复亨之子。于朱子为再从亲。而朱子称允夫为内弟。汪尚书应辰为朱子外祖妹子。而朱子自称以表侄。此古人之忠厚质实处也。
弟。而朱子撰其行状及祭文。皆称叔祖。自称从孙。程允夫为韦斋内弟复亨之子。于朱子为再从亲。而朱子称允夫为内弟。汪尚书应辰为朱子外祖妹子。而朱子自称以表侄。此古人之忠厚质实处也。杜氏通典。晋蔡谟曰。前母之党。应为亲不疑。惠帝时尚书令满武秋是曹彦真前母之兄。而不为内外之亲。相见如他人。吾昔以问江思悛。悛以为人不疑继母之党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继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与其党为亲。何至前母而独疑之。吾谓此言。是朱子撰何叔京墓碣。称其继母邓氏兄邓柞为邓舅。石子重墓志。称其继母陈氏兄良翰为舅氏。世之处前母继母之党者。据此称亲。庶或寡过矣。
律中不许姑舅之子为婚。而黄辂以朱子外孙为孙婿。盖自春秋之世。列国世为婚姻。其间多有姑舅之子者。汉晋以来。亦多有之。此礼终古已然。而宋仁宗之女。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欧阳公云公私皆已通行。盖宋时此礼已为上下通行之例。故朱子亦从之也。
杨仲思问处乡党宗族。见他有碍理不安处。且欲与之和同则又不便。欲正己以远之。又失之孤介而不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538H 页
 合中道。如何。朱子曰。这般处也是难。只得无忿疾之心尔。按乡党固是父兄宗族之所在。然仲思既并举乡党宗族。则二者固有别矣。其处之之道。恐亦当有间。宗族中有碍理不安处。当尽吾诚意。晓之以义理。若不听是小小碍理事。则亦无可柰何。若是大害事。则不可以其不听而遽止。务在积渐浸灌。期于救正而后已。乡党中有碍理不安处。亦当尽吾之心。晓之以义理。若不听则只合闭门自修。决不可与之和同也。
合中道。如何。朱子曰。这般处也是难。只得无忿疾之心尔。按乡党固是父兄宗族之所在。然仲思既并举乡党宗族。则二者固有别矣。其处之之道。恐亦当有间。宗族中有碍理不安处。当尽吾诚意。晓之以义理。若不听是小小碍理事。则亦无可柰何。若是大害事。则不可以其不听而遽止。务在积渐浸灌。期于救正而后已。乡党中有碍理不安处。亦当尽吾之心。晓之以义理。若不听则只合闭门自修。决不可与之和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