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书
书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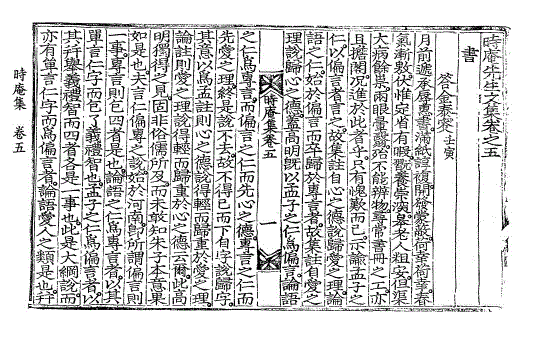 答金泰叟(壬寅)
答金泰叟(壬寅)月前递承辱惠书。满纸谆复。开发蒙蔽。荷幸荷幸。春气渐敷。伏惟定省有暇。玩养崇深。皋老人粗安。但渠大病馀祟。两眼晕翳。殆不能辨物。寻常书册之工。亦且担阁。况进于此者乎。只有愧叹而已。示谕孟子之仁。以偏言者言之。故集注自心之德说归爱之理。论语之仁。始于偏言而卒归于专言者。故集注自爱之理说归心之德。盖高明既以孟子之仁为偏言。论语之仁为专言。而偏言之仁而先心之德。专言之仁而先爱之理。终是说不去。故不得已而下自字说归字。其意以为孟注则心之德说得轻而归重于爱之理。论注则爱之理说得轻而归重于心之德云尔。此高明独得之见。固非俗儒所及。而未敢知朱子本意果如是也。夫言仁偏专之说。始于河南。即所谓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也。论语之仁为专言者。以其单言仁字而包了义礼智也。孟子之仁为偏言者。以其并举义礼智而四者各是一事也。此是大纲说。而亦有单言仁字而为偏言者。论语爱人之类是也。并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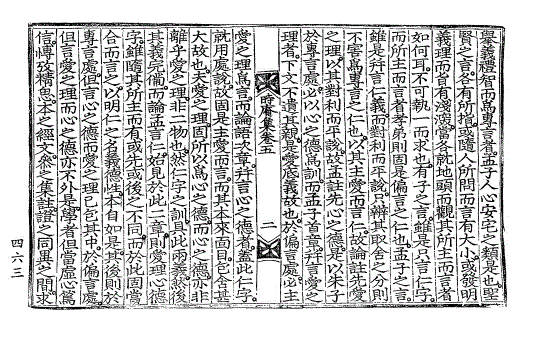 举义礼智而为专言者。孟子人心安宅之类是也。圣贤之言。各有所指。或随人所问而言有大小。或发明义理而旨有浅深。当各就地头而观其所主而言者如何耳。不可执一而求也。有子之言。虽是只言仁字。而所主而言者孝弟则固是偏言之仁也。孟子之言。虽是并言仁义。而对利而平说。只辨其取舍之分则不害为专言之仁也。以其主爱而言仁。故论注先爱之理。以其对利而平说。故孟注先心之德。是以朱子于专言处。必以心之德为训。而孟子首章。并言爱之理者。下文不遗其亲。是爱底义故也。于偏言处。必主爱之理为言。而论语次章。并言心之德者。盖此仁字。就用处说。故固是主爱而言。而其本来面目。包含甚大故也。夫爱之理。固所以为心之德。而心之德。亦非离乎爱之理。非二物也。然仁字之训。具此两义。然后其义完备。而论孟言仁。始见于此二章。则爱理心德字。虽随其所主而有或先或后之不同。而于此固当合而言之。以明仁之名义德性。本自如是。其后则于专言处。但言心之德而爱之理已包其中。于偏言处。但言爱之理而心之德亦不外是。学者但当虚心笃信。博考精思。本之经文。参之集注。證之同异之间。求
举义礼智而为专言者。孟子人心安宅之类是也。圣贤之言。各有所指。或随人所问而言有大小。或发明义理而旨有浅深。当各就地头而观其所主而言者如何耳。不可执一而求也。有子之言。虽是只言仁字。而所主而言者孝弟则固是偏言之仁也。孟子之言。虽是并言仁义。而对利而平说。只辨其取舍之分则不害为专言之仁也。以其主爱而言仁。故论注先爱之理。以其对利而平说。故孟注先心之德。是以朱子于专言处。必以心之德为训。而孟子首章。并言爱之理者。下文不遗其亲。是爱底义故也。于偏言处。必主爱之理为言。而论语次章。并言心之德者。盖此仁字。就用处说。故固是主爱而言。而其本来面目。包含甚大故也。夫爱之理。固所以为心之德。而心之德。亦非离乎爱之理。非二物也。然仁字之训。具此两义。然后其义完备。而论孟言仁。始见于此二章。则爱理心德字。虽随其所主而有或先或后之不同。而于此固当合而言之。以明仁之名义德性。本自如是。其后则于专言处。但言心之德而爱之理已包其中。于偏言处。但言爱之理而心之德亦不外是。学者但当虚心笃信。博考精思。本之经文。参之集注。證之同异之间。求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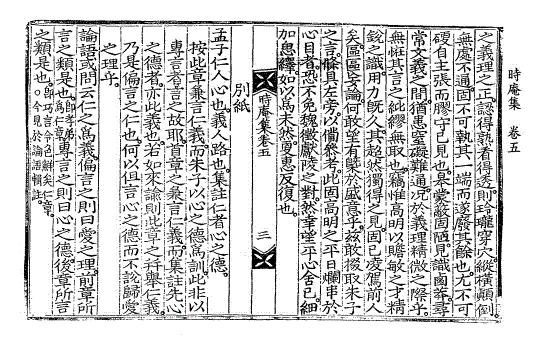 之义理之正。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固不可执其一端而遂废其馀也。尤不可硬自主张而胶守己见也。皋蒙蔽固陋。见识卤莽。寻常文义之间。犹患窒碍难通。况于义理精微之际乎。无怪其言之纰缪无取也。窃惟高明以赡敏之才精锐之识。用力既久。其超然独得之见。固已凌驾前人矣。区区妄论。何敢望有槩于盛意乎。玆敢掇取朱子之言。条具左旁。以备参考。此固高明之平日烂串于心目者。恐不免魏徵献陵之对。然幸望平心舍己。细加思绎。如以为未然。更惠反复也。
之义理之正。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固不可执其一端而遂废其馀也。尤不可硬自主张而胶守己见也。皋蒙蔽固陋。见识卤莽。寻常文义之间。犹患窒碍难通。况于义理精微之际乎。无怪其言之纰缪无取也。窃惟高明以赡敏之才精锐之识。用力既久。其超然独得之见。固已凌驾前人矣。区区妄论。何敢望有槩于盛意乎。玆敢掇取朱子之言。条具左旁。以备参考。此固高明之平日烂串于心目者。恐不免魏徵献陵之对。然幸望平心舍己。细加思绎。如以为未然。更惠反复也。别纸
孟子仁人心也。义人路也。集注仁者心之德。
按此章兼言仁义。而朱子以心之德为训。此非以专言者言之故耶。首章之兼言仁义。而集注先心之德者。亦此义也。若如来谕则此章之并举仁义。乃是偏言之仁也。何以但言心之德而不说归爱之理乎。
论语或问云仁之为义。偏言之则曰爱之理。前章所言之类是也。(即孝弟为仁章。)专言之则曰心之德。后章所言之类是也。(即巧言令色鲜矣仁章。○今见于论语辑注。)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4L 页
 大全答张敬夫书论孝弟为仁之本注曰。此章仁字。正指爱之理而言。即易传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
大全答张敬夫书论孝弟为仁之本注曰。此章仁字。正指爱之理而言。即易传所谓偏言则一事者也。语类问孝弟为仁之本曰。这个仁。是爱底意思。是偏言底。不是专言底。
按此三说。朱子既以此仁字断以为偏言之仁。而未尝言卒归于专言。又曰正指爱之理而言。而未尝以心之德为主。则来谕所谓自爱之理说归心之德者。无乃与朱子本意相背乎。
大全答欧阳希逊书曰。恻隐之类。偏言之也。克己之类。专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盖亦非二物也。故论语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此言极有味。不可谓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遍。孟子亦有专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爱人是也。孔子虽不以义对仁。然每以智对仁。
按此所谓论语集注中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者。即克己为仁章集注初本也。盖克己之仁。是专言者。故曰心之德爱之理。此处亦可谓自心之德说归爱之理乎。以此推彼则朱子之意可见也。然朱子之不用初本而改以本心之全德者。盖此仁字从克己复礼上说。则己者私欲也。礼者天理也。胜私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5H 页
 欲而复天理。则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本心之德既全。则爱之理固在其中。然此处只可曰心之德以包之。而爱之字犹有偏底意故也。朱子之训。一字不苟。先后增损之间。皆有深意如此。幸望于此细入思量。反复参订。则以高明明睿之见。虚受之量。想必焕然冰释而不待其辞之毕矣。
欲而复天理。则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本心之德既全。则爱之理固在其中。然此处只可曰心之德以包之。而爱之字犹有偏底意故也。朱子之训。一字不苟。先后增损之间。皆有深意如此。幸望于此细入思量。反复参订。则以高明明睿之见。虚受之量。想必焕然冰释而不待其辞之毕矣。万正淳问。集注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其言之不一何也。盖仁有偏言者。有专言者。专言者心之德。偏言者爱之理云云。答曰。固是如此。然心之德。即爱之理。非二物。但所从言之异耳。
按万氏所疑言之不一者。盖谓心德爱理字之或先或后也。专言故先心之德。偏言故先爱之理。此所谓所从言之异耳。
语类其为人也孝弟章。心之德爱之理云云。
按据此则集注初本。盖先言心之德而后言爱之理。其先爱理而后心德。恐是改本也。盖朱子初意以为论语之仁。皆是专言者。故先心德而后爱理。既而见得此仁字主孝弟说。则毕竟是偏言底。故改以爱之理心之德也。其旨益以明矣。
仁兼义言者是言体。专言者是兼体用而言。(此条已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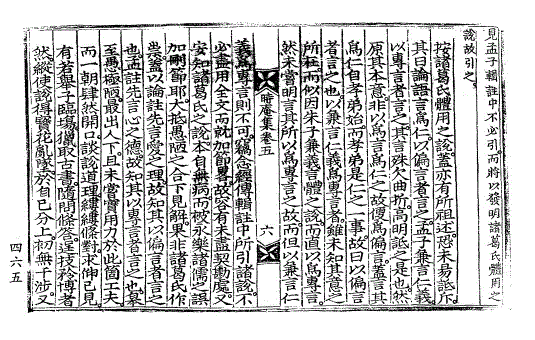 见孟子辑注中不必引。而将以发明诸葛氏体用之说故引之。)
见孟子辑注中不必引。而将以发明诸葛氏体用之说故引之。)按诸葛氏体用之说。盖亦有所祖述。恐未易诋斥。其曰论语言为仁。以偏言者言之。孟子兼言仁义。以专言者言之。其言殊欠曲折。高明诋之是也。然原其本意。非以为言为仁之故便为偏言。盖言其为仁自孝弟始。而孝弟是仁之一事。故曰以偏言者言之也。以兼言仁义为专言者。虽未知其意之所在。而似因朱子兼义言体之说。而直以为专言。然未尝明言其所以为专言之故。而但以兼言仁义为专言则不可。窃念经传辑注中所引诸说。不必尽用全文而就加节略。故容有未尽契勘处。又安知诸葛氏之说。本自无病。而被永樂诸儒之误加删节耶。大抵愚陋之合下见解。果非诸葛氏作祟。盖以论注先言爱之理。故知其以偏言者言之也。孟注先言心之德。故知其以专言者言之也。皋至愚极陋。最出人下。且未尝实用力于此个工夫。而一朝肆然开口。谈说道理。縷縷条对。求伸己见。有若举子临场。猎取古书。随问条答。逞技矜博者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于自己分上。初无干涉。又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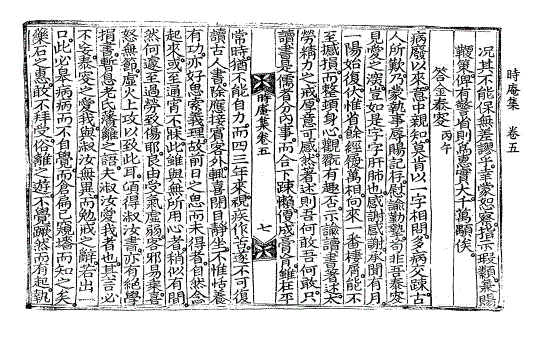 况其不能保无差谬乎。幸蒙恕察。指示瑕颣。兼赐鞭策。俾有警省则为惠实大。千万颙俟。
况其不能保无差谬乎。幸蒙恕察。指示瑕颣。兼赐鞭策。俾有警省则为惠实大。千万颙俟。答金泰叟(丙午)
病废以来。意中亲知。莫肯以一字相问。多病交疏。古人所叹。乃蒙执事辱赐记存。慰谕勤挚。苟非吾泰叟见爱之深。岂如是字字肝肺也。感谢感谢。承闻有月。一阳始复。伏惟省馀经履万相。向来一番栖屑。能不至撼损。而整顿身心。观玩有趣否。示谕读书著述。太劳精力之戒。厚意可感。然著述则吾何敢吾何敢。只读书是儒者分内事。而合下疏懒。便成膏肓。虽在平常时。犹不能自力。而四三年来。视疾作苦。遂不可复读古人书。除应接宾客外。辄喜闭目静坐。不惟恬养有功。亦好思索义理。故前日之思而未得者。自然念起来。或至通宵不寐。此虽与无所用心者。稍似有间。然何遽至过劳致伤耶。良由受气虚弱。客邪易乘。喜怒无节。虚火上攻以致此耳。顷得淑汝书。亦有绝学捐书。暂息老氏藩篱之语。夫淑汝爱我者也。其言必不妄。泰叟之爱我。与淑汝无异。而勉戒之辞。若出一口。此必皋病病而不自觉。而仓扁已窥墙而知之矣。药石之惠。敢不拜受。俗离之游。不觉蹶然而有起。执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6L 页
 事之康健。办得此一奇事容易。顾此跧蛰穷庐。出不得门前一步地者。真是黄鹄之与壤虫。健羡健羡。此行必有纪咏诸作。或望因便投示。豁此病怀否。濯叟之名登荐剡。可见公议之尚在。闻已赴 召云。未知已 肃谢而归耶。抑濡滞京邸耶。念其亲老在堂。不得不为禄仕计。然此路一出。瞿塘在前。未尝不为渠有过计之忧也。淑汝之归。差强人意。
事之康健。办得此一奇事容易。顾此跧蛰穷庐。出不得门前一步地者。真是黄鹄之与壤虫。健羡健羡。此行必有纪咏诸作。或望因便投示。豁此病怀否。濯叟之名登荐剡。可见公议之尚在。闻已赴 召云。未知已 肃谢而归耶。抑濡滞京邸耶。念其亲老在堂。不得不为禄仕计。然此路一出。瞿塘在前。未尝不为渠有过计之忧也。淑汝之归。差强人意。与金泰叟(癸亥)
昨夏寒坪之拜。人事稠扰。未得稳叙积抱。馀怅尚尔未化。伏惟春和。经履节宣康福。玩养崇深。皋衰病侵凌。旧业荒废。秖自悼叹。范义雠校之役。病未得参听于诸贤之后。实为愧恨。而谨阅校本。正误补阙。考据精核。义例整当。至如题注总论之或删或合。数三诸条之易置类从。其他九经或问小学题辞之添补。尤见用意之勤。殊庸叹服。愚陋浅见。亦尝妄疑采摭之际。不免或有漏阙。类例之间。亦有未尽梳洗处。前答仲车书。略陈鄙见。想已俯谅矣。近读大山先生答冷泉李公书。乃知前辈之于此事。其难慎如此。区区所疑。真是僭妄。且鄙乡佥议皆以为是书屡经先辈是正。无复遗憾。以仍旧本入梓为正。固是慎重底道理。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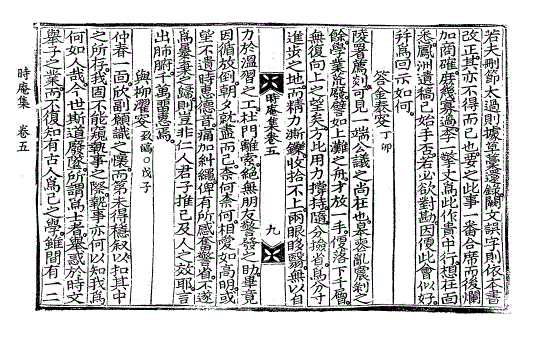 若夫删节太过则据草稿还录。阙文误字则依本书改正。其亦不得而已也。要之此事一番合席而后烂加商确。庶几寡过。李一擎丈为此作贵中行。想在面悉。凤洲遗稿已始手否。若必欲对勘。因便此会似好。并为回示如何。
若夫删节太过则据草稿还录。阙文误字则依本书改正。其亦不得而已也。要之此事一番合席而后烂加商确。庶几寡过。李一擎丈为此作贵中行。想在面悉。凤洲遗稿已始手否。若必欲对勘。因便此会似好。并为回示如何。答金泰叟(丁卯)
陵署荐剡。可见一端公议之尚在也。皋丧乱震剥之馀。学业荒废。譬如上滩之舟。才放一手。便落下千层。无复向上之望矣。方此用力撑持。随分捡省。为分寸进步之地。而精力澌铄。收拾不上。两眼眵翳。无以自力于温习之工。杜门离索。绝无朋友警发之助。毕竟因循放倒。朝夕就尽而已。柰何柰何。相爱如高明。或望不遗时惠德音。痛加纠绳。俾有所感奋警省。不遂为㬥弃之归。则岂非仁人君子推己及人之效耶。言出肺腑。千万留惠焉。
与柳濯叟(致皓○戊子)
仲春一面。欣副愿识之怀。而第未得稳叙。以扣其中之所存。我固不能窥执事之际。执事亦何以知我为何如人哉。今世斯道废坠。所谓为士者。举惑于时文举子之业。而不复知有古人为己之学。虽间有一二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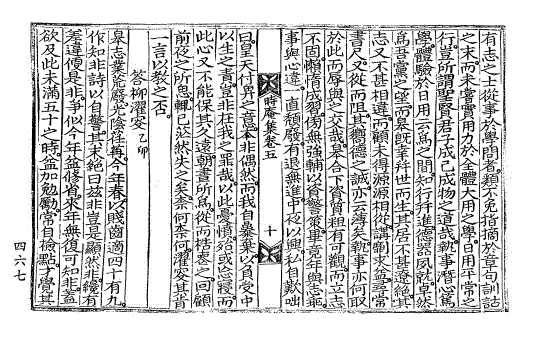 有志之士从事于学问者。类不免指摘于章句训诂之末。而未尝实用力于全体大用之学。日用平常之行。岂所谓圣贤君子成己成物之道哉。执事潜心笃学。体验于日用云为之间。知行并进。德器夙就。卓然为吾党之望。而皋既幸并世而生。其居不甚辽绝。其志又不甚相违。而顾未得源源相从。讲劘求益。寻常书尺。又从而阻。其向德之诚。亦云薄矣。执事亦何取于此而辱与之交哉。皋合下资质粗有可观。而立志不固。懒惰成习。傍无强辅以资警策。毕竟年与志乖。事与心违。一直颓废。有退无进。中夜以兴。私自叹咄曰。皇天付畁之意。本非偶然。而我自㬥弃。以负受中以生之责。岂非在我之罪哉。以此忧愤。殆或忘寝。而此心又不能保其久远。朝昼所为。从而梏丧之。回顾前夜之所思。辄已茫然失之矣。柰何柰何。濯叟其肯一言以教之否。
有志之士从事于学问者。类不免指摘于章句训诂之末。而未尝实用力于全体大用之学。日用平常之行。岂所谓圣贤君子成己成物之道哉。执事潜心笃学。体验于日用云为之间。知行并进。德器夙就。卓然为吾党之望。而皋既幸并世而生。其居不甚辽绝。其志又不甚相违。而顾未得源源相从。讲劘求益。寻常书尺。又从而阻。其向德之诚。亦云薄矣。执事亦何取于此而辱与之交哉。皋合下资质粗有可观。而立志不固。懒惰成习。傍无强辅以资警策。毕竟年与志乖。事与心违。一直颓废。有退无进。中夜以兴。私自叹咄曰。皇天付畁之意。本非偶然。而我自㬥弃。以负受中以生之责。岂非在我之罪哉。以此忧愤。殆或忘寝。而此心又不能保其久远。朝昼所为。从而梏丧之。回顾前夜之所思。辄已茫然失之矣。柰何柰何。濯叟其肯一言以教之否。答柳濯叟(乙卯)
皋志业荒废。光阴荏苒。今年春。以贱齿适四十有九。作知非诗以自警。其末绝曰玆非岂是显然非。才有差违便是非。争似今年益修省。来年无复可知非。盖欲及此未满五十之时。益加勉励。常自检点。才觉其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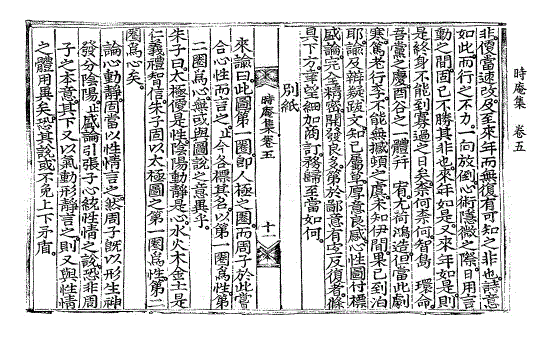 非。便当速改。及至来年而无复有可知之非也。诗意如此。而行之不力。一向放倒。心术隐微之际。日用言动之间。固已不胜其非也。来年如是。又来年如是。则是终身不能到寡过之日矣。柰何柰何。智岛 环命。吾党之庆。酉谷之一体并 宥。尤荷鸿造。但当此剧寒。笃老行李。不能无撼顿之虞。未知伊间。果已到泊耶。谕及辨疑跋文。知已属草。厚意良感。心性图付标盛论。完全精密。开发良多。第于鄙意有宜反复者。条具下方。幸望细加商订。务归至当如何。
非。便当速改。及至来年而无复有可知之非也。诗意如此。而行之不力。一向放倒。心术隐微之际。日用言动之间。固已不胜其非也。来年如是。又来年如是。则是终身不能到寡过之日矣。柰何柰何。智岛 环命。吾党之庆。酉谷之一体并 宥。尤荷鸿造。但当此剧寒。笃老行李。不能无撼顿之虞。未知伊间。果已到泊耶。谕及辨疑跋文。知已属草。厚意良感。心性图付标盛论。完全精密。开发良多。第于鄙意有宜反复者。条具下方。幸望细加商订。务归至当如何。别纸
来谕曰。此图第一圈。即人极之圈。而周子于此尝合心性而言之。(止。)今各标其名。以第一圈为性。第二圈为心。无或与图说之意异乎。
朱子曰。太极便是性。阴阳动静是心。水火木金土是仁义礼智信。朱子固以太极图之第一圈为性。第二圈为心矣。
论心动静。固当以性情言之。然周子既以形生神发分阴阳。(止。)盛论引张子心统性情之说。恐非周子之本意。其下又以气动形静言之。则又与性情之体用异矣。恐其说或不免上下矛盾。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8L 页
 周子所谓形生神发。主阴阳而言。张子所谓心统性情。合理气而言。二说虽若不同。而其实则一也。若非无极之真。为之枢纽根柢。则所谓形与神者。何自而生且发乎。盖此图第二圈中圆圈即性也。阴阳动静者情也。合而言之则心也。故引张子此说。以解全圈之体。其下又分解中圈与左右两圈。一如朱子解剥图体之例。其曰气之动也。心之用所以行也。形之静也。心之体所以立也者。非以气动形静。便为心之体用。乃心之体用。所以立所以行也。须看所以字。(太极图解。太极之用所以行。太极之体所以立。其义本自如是。若以阴静便为太极之体。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夫心之体即性也。心之用即情也。则与所谓性情体用之说。恐不至大相矛盾矣。如何如何。其以引张子说。谓非图说之本意者。窃恐未然。夫圣贤之言。虽有彼此之不同。而其理则未尝不一。故朱子尝以张子此说为有合于周子之旨。(不记全文而大意如此。)恐非偶然。程张本然气质之论。虽曰发前人所未发。盖亦有所祖述。朱子所谓程子之言性与天道多出于此者。其非指此等处而言欤。
周子所谓形生神发。主阴阳而言。张子所谓心统性情。合理气而言。二说虽若不同。而其实则一也。若非无极之真。为之枢纽根柢。则所谓形与神者。何自而生且发乎。盖此图第二圈中圆圈即性也。阴阳动静者情也。合而言之则心也。故引张子此说。以解全圈之体。其下又分解中圈与左右两圈。一如朱子解剥图体之例。其曰气之动也。心之用所以行也。形之静也。心之体所以立也者。非以气动形静。便为心之体用。乃心之体用。所以立所以行也。须看所以字。(太极图解。太极之用所以行。太极之体所以立。其义本自如是。若以阴静便为太极之体。则是未免认气为理之病。)夫心之体即性也。心之用即情也。则与所谓性情体用之说。恐不至大相矛盾矣。如何如何。其以引张子说。谓非图说之本意者。窃恐未然。夫圣贤之言。虽有彼此之不同。而其理则未尝不一。故朱子尝以张子此说为有合于周子之旨。(不记全文而大意如此。)恐非偶然。程张本然气质之论。虽曰发前人所未发。盖亦有所祖述。朱子所谓程子之言性与天道多出于此者。其非指此等处而言欤。第三圈之交系。恐当以阴阳之互根言之。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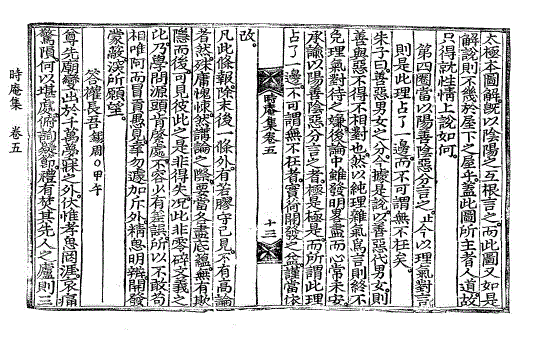 太极本图解。既以阴阳之互根言之。而此图又如是解说则不几于屋下之屋乎。盖此图所主者人道。故只得就性情上说如何。
太极本图解。既以阴阳之互根言之。而此图又如是解说则不几于屋下之屋乎。盖此图所主者人道。故只得就性情上说如何。第四圈当以阳善阴恶分言之。(止。)今以理气对言。则是此理占了一边。而不可谓无不在矣。
朱子曰。善恶男女之分。今据是说。以善恶代男女。则善与恶不得不相对也。然以纯理杂气为言则终不免理气对待之嫌。后论中虽发明略尽而心常未安。承谕以阳善阴恶分言之者。极是极是。而所谓此理占了一边。不可谓无不在者。实荷开发之益。谨当依改。
凡此条报。除末后一条外。有若胶守己见。不有高论者然。殊庸愧悚。然讲论之际。要当各尽底蕴。无有欺隐而后。可见彼此之是非得失。况此非零碎文义之比。乃学问源头肯綮处。不容少有差误。所以不敢苟相唯阿而冒贡愚见。幸勿遽加斥外。精思明辨。开发蒙蔽。深所愿望。
答权长吾(锡周○甲午)
尊先庙变出于千万梦寐之外。伏惟孝思罔涯。哀痛惊陨。何以堪处。俯询疑节。礼有焚其先人之庐则三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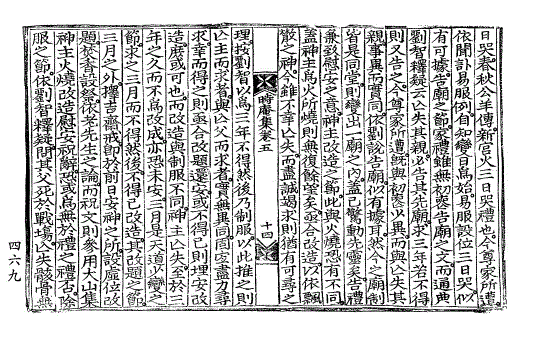 日哭。春秋公羊传。新宫火三日哭礼也。今尊家所遭。依闻讣易服例。自知变日为始。易服设位三日哭。似有可据。告庙之节。家礼虽无初丧告庙之文。而通典刘智释疑云亡失其亲。必告其先庙。求三年若不得则又告之。今尊家所遭。既与初丧少异。而与亡失其亲。事异而实同。依刘说告庙。似有据耳。然今之庙制皆是同堂。则变出一庙之内。盖已惊动先灵矣。告礼兼致慰安之意。神主改造之节。此与火烧恐有不同。盖神主为火所烧则无复馀望矣。亟合改造。以依飘散之神。今虽不幸亡失。而尽诚竭求则犹有可寻之理。按刘智以为三年不得然后乃制服。以此推之则亡主而求者。与亡父而求者。实无异同。固宜尽力寻求。幸而得之则亟合改题还安。或不得已则埋安改造。庶或可也。而改造与制服不同。神主亡失。至于三年之久而不为改成。亦恐未安。三月是天道少变之节。求之三月而不得然后。不得已改造。其改题之节。三月之外。择吉斋戒。即于前日安神之所。设虚位改题。焚香设祭。依老先生之论。而祝文则参用大山集神主火烧改造慰安祝辞。恐或为无于礼之礼否。除服之节。依刘智释疑。问其父死于战场。亡失骸骨无
日哭。春秋公羊传。新宫火三日哭礼也。今尊家所遭。依闻讣易服例。自知变日为始。易服设位三日哭。似有可据。告庙之节。家礼虽无初丧告庙之文。而通典刘智释疑云亡失其亲。必告其先庙。求三年若不得则又告之。今尊家所遭。既与初丧少异。而与亡失其亲。事异而实同。依刘说告庙。似有据耳。然今之庙制皆是同堂。则变出一庙之内。盖已惊动先灵矣。告礼兼致慰安之意。神主改造之节。此与火烧恐有不同。盖神主为火所烧则无复馀望矣。亟合改造。以依飘散之神。今虽不幸亡失。而尽诚竭求则犹有可寻之理。按刘智以为三年不得然后乃制服。以此推之则亡主而求者。与亡父而求者。实无异同。固宜尽力寻求。幸而得之则亟合改题还安。或不得已则埋安改造。庶或可也。而改造与制服不同。神主亡失。至于三年之久而不为改成。亦恐未安。三月是天道少变之节。求之三月而不得然后。不得已改造。其改题之节。三月之外。择吉斋戒。即于前日安神之所。设虚位改题。焚香设祭。依老先生之论。而祝文则参用大山集神主火烧改造慰安祝辞。恐或为无于礼之礼否。除服之节。依刘智释疑。问其父死于战场。亡失骸骨无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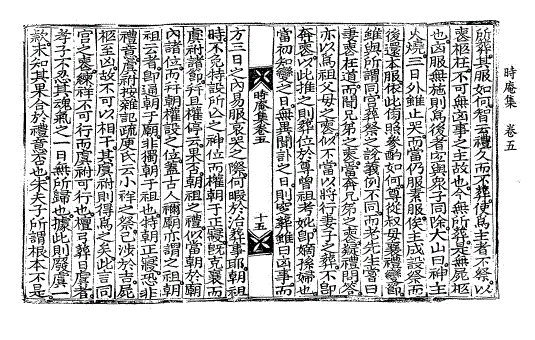 所葬。其服如何。智云礼久而不葬。使为主者不祭。以丧柩在。不可无凶事之主故也。今无所葬。是无尸柩也。凶服无施则为后者宜与众子同除。大山曰。神主火烧。三日外虽止哭。而当仍服素服。俟主成设祭而后还本服。依此傍照参酌如何。尊从叔母襄礼变节。虽与所谓同宫葬祭之说义例不同。而老先生尝曰妻丧在道。而闻兄弟之丧。当奔兄弟之丧。疑礼问答。亦以为祖父母之丧。似不当以将行妻子之葬。不即奔丧。以此推之则葬位于尊曾祖考妣。即嫡孙妇也。当初知变之日。无异闻讣之日。则窆葬虽曰凶事。而方三日之内易服哀哭之际。何暇于治葬事耶。朝祖时。不免特设所亡之神位而权朝于正寝。既克襄而虞祔诸节。并且权停云。果否。朝祖之礼。似当朝于庙内诸位。而并朝权设之位。盖古人祢庙亦谓之祖。朝祖云者。即通朝于庙。非独朝于祖也。特朝正寝。恐非礼意。虞祔按杂记疏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则得为之矣。此言同宫之丧。练祥不可行而虞祔可行也。檀弓葬日虞者。孝子不忍其魂气之一日无所归也。据此则废虞一款。未知其果合于礼意否也。朱夫子所谓根本不是。
所葬。其服如何。智云礼久而不葬。使为主者不祭。以丧柩在。不可无凶事之主故也。今无所葬。是无尸柩也。凶服无施则为后者宜与众子同除。大山曰。神主火烧。三日外虽止哭。而当仍服素服。俟主成设祭而后还本服。依此傍照参酌如何。尊从叔母襄礼变节。虽与所谓同宫葬祭之说义例不同。而老先生尝曰妻丧在道。而闻兄弟之丧。当奔兄弟之丧。疑礼问答。亦以为祖父母之丧。似不当以将行妻子之葬。不即奔丧。以此推之则葬位于尊曾祖考妣。即嫡孙妇也。当初知变之日。无异闻讣之日。则窆葬虽曰凶事。而方三日之内易服哀哭之际。何暇于治葬事耶。朝祖时。不免特设所亡之神位而权朝于正寝。既克襄而虞祔诸节。并且权停云。果否。朝祖之礼。似当朝于庙内诸位。而并朝权设之位。盖古人祢庙亦谓之祖。朝祖云者。即通朝于庙。非独朝于祖也。特朝正寝。恐非礼意。虞祔按杂记疏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则得为之矣。此言同宫之丧。练祥不可行而虞祔可行也。檀弓葬日虞者。孝子不忍其魂气之一日无所归也。据此则废虞一款。未知其果合于礼意否也。朱夫子所谓根本不是。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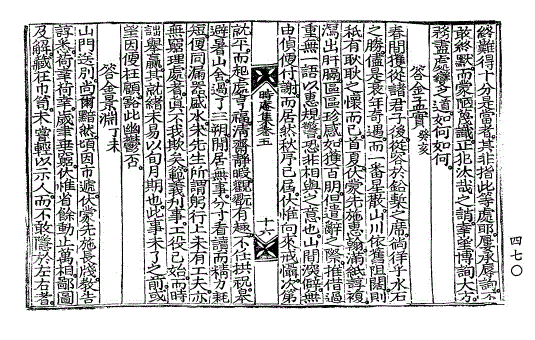 终难得十分是当者。其非指此等处耶。屡承辱询。不敢终默。而蒙陋蔑识。正犯汰哉之诮。幸望博询大方。务尽处变之道。如何如何。
终难得十分是当者。其非指此等处耶。屡承辱询。不敢终默。而蒙陋蔑识。正犯汰哉之诮。幸望博询大方。务尽处变之道。如何如何。答金孟实(癸亥)
春间获从诸君子后。从容于铅椠之席。徜徉乎水石之胜。尽是衰年奇遇。而一番星散。山川依旧阻阔。则秖有耿耿之怀而已。首夏。伏蒙先施惠翰。满纸谆复。泻出肝膈。区区珍感。如获百朋。但遣辞之际。推借过重。无一语以惠规警。恐非相与之意也。山间深僻。无由侦便付谢。而居然秋序已届。伏惟向来戒慑。次第就平。而起处亨福。清斋静暇。观玩有趣。不任拱祝。皋避暑山舍。过了三朔。閒居无事。分寸看读而精力耗短。便同漏器盛水。朱先生所谓躬行上未有工夫。亦无穷理处者。真不我欺矣。范义刊事。工役已始。而时诎举赢。其就绪未易以旬月期也。此事未了之前。或望因便枉顾。豁此幽郁否。
答金景渊(丁未)
山门送别。尚尔黯然。顷因市递。伏蒙先施长笺。教告谆悉。荷幸荷幸。岁聿垂穷。伏惟省馀动止万相。鄙图及解。藏在巾笥。未尝轻以示人。而不敢隐于左右者。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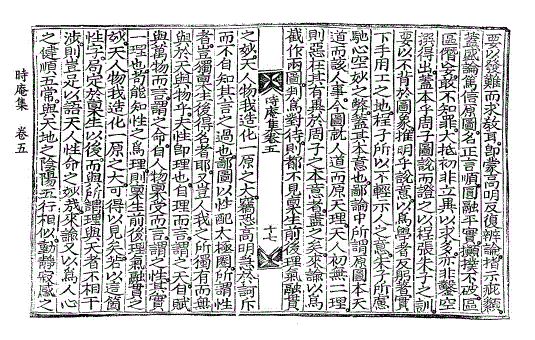 要以发难而求教耳。即蒙高明反复辨论。指示疵颣。盖盛论笃信原图。名正言顺。圆融平实。攧扑不破。区区僭妄。敢不知罪。大抵初非立异以求多。亦非凿空撰得出。盖本乎周子图说而證之以程张朱子之训。要以不背于图象。推明乎说意。以为学者反躬著实下手用工之地。程子所以不轻示人之意。朱子所虑驰心空妙之弊。盖其本意也。鄙论中所谓原图本天道而该人事。今图就人道而原天理。天人初无二理。则恶在其有异于周子之本意者。尽之矣。来谕以为截作两图。判为对待。则都不见禀生前后理气融贯之妙。天人物我造化一原之大。窃恐高明急于诃斥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鄙图以性配太极圈。所谓性者。岂独禀生后得名者耶。又岂人我之所独有而无与于天与物乎。夫性即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赋与万物而言。谓之命。自人物禀受而言。谓之性。其实一理也。苟能知性之为理。则禀生前后理气融贯之妙。天人物我造化一原之大。可得以见矣。若以这个性字。局定于禀生以后。而与所谓理与天者不相干涉。则岂足以语天人性命之妙哉。来谕又以为人心之健顺五常。与天地之阴阳五行相似。动静寂感之
要以发难而求教耳。即蒙高明反复辨论。指示疵颣。盖盛论笃信原图。名正言顺。圆融平实。攧扑不破。区区僭妄。敢不知罪。大抵初非立异以求多。亦非凿空撰得出。盖本乎周子图说而證之以程张朱子之训。要以不背于图象。推明乎说意。以为学者反躬著实下手用工之地。程子所以不轻示人之意。朱子所虑驰心空妙之弊。盖其本意也。鄙论中所谓原图本天道而该人事。今图就人道而原天理。天人初无二理。则恶在其有异于周子之本意者。尽之矣。来谕以为截作两图。判为对待。则都不见禀生前后理气融贯之妙。天人物我造化一原之大。窃恐高明急于诃斥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鄙图以性配太极圈。所谓性者。岂独禀生后得名者耶。又岂人我之所独有而无与于天与物乎。夫性即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赋与万物而言。谓之命。自人物禀受而言。谓之性。其实一理也。苟能知性之为理。则禀生前后理气融贯之妙。天人物我造化一原之大。可得以见矣。若以这个性字。局定于禀生以后。而与所谓理与天者不相干涉。则岂足以语天人性命之妙哉。来谕又以为人心之健顺五常。与天地之阴阳五行相似。动静寂感之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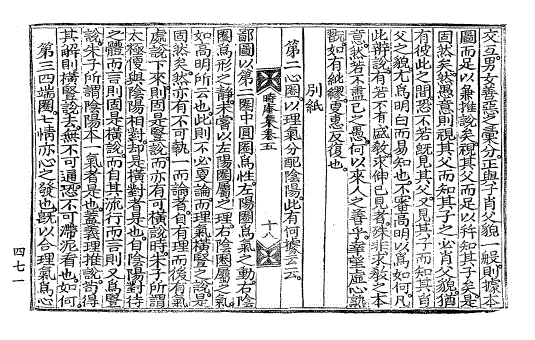 交互。男女善恶之汇分。正与子肖父貌一般。则据本图而足以兼推说矣。视其父而足以并知其子矣。是固然矣。然愚意则视其父而知其子之必肖父貌。犹有彼此之间。恐不若既见其父。又见其子而知其肖父之貌。尤为明白而易知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凡此辨说。有若不有盛教。求伸己见者。殊非求教之本意。然若不尽己之愚。何以来人之善乎。幸望虚心熟玩。如有纰缪。更惠反复也。
交互。男女善恶之汇分。正与子肖父貌一般。则据本图而足以兼推说矣。视其父而足以并知其子矣。是固然矣。然愚意则视其父而知其子之必肖父貌。犹有彼此之间。恐不若既见其父。又见其子而知其肖父之貌。尤为明白而易知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凡此辨说。有若不有盛教。求伸己见者。殊非求教之本意。然若不尽己之愚。何以来人之善乎。幸望虚心熟玩。如有纰缪。更惠反复也。别纸
第二心圈。以理气分配阴阳。此有何据云云。
鄙图以第二圈中圆圈为性。左阳圈为气之动。右阴圈为形之静。未尝以左阳圈属之理。右阴圈属之气。如高明所云也。此则不必更论。而理气横竖之说。是固然矣。然亦有不可执一而论者。自有理而后有气处说下来。则固是竖说。而亦有可横说时。朱子所谓太极便与阴阳相对。却是横对者是也。自阴阳对待之体而言则固是横说。而自其流行而言则又为竖说。朱子所谓阴阳本一气者是也。盖义理推说。苟得其解则横竖说去。无不可通。恐不可滞泥看也。如何。
第三四端圈。七情亦心之发也。既以合理气为心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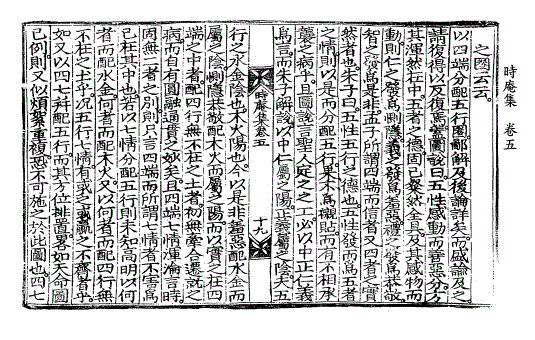 之圈云云。
之圈云云。以四端分配五行圈。鄙解及后论详矣。而盛谕及之。请复得以反复焉。盖图说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方其浑然在中。五者之德。固已粲然全具。及其感物而动。则仁之发为恻隐。义之发为羞恶。礼之发为恭敬。智之发为是非。孟子所谓四端而信者又四者之实然者也。朱子曰。五性五行之德也。五性发而为五者之情。则以是而分配五行。果不为衬贴。而有不相承袭之病乎。且图说言圣人定之之工。必以中正仁义为言。而朱子解说。以中仁属之阳。正义属之阴。夫五行之水金阴也。木火阳也。今以是非羞恶配水金而属之阴。恻隐恭敬配木火而属之阳。而以实之在四端之中者。配四行无不在之土者。初无牵合迁就之病。而自有圆融通贯之妙矣。且四端七情浑沦言时。固无二者之别。则只言四端而所谓七情者不害为已在其中也。若以七情分配五行则未知高明以何者而配水金。何者而配木火。又以何者而配四行无不在之土乎。况五行七情。有或乏或赢之不齐者乎。如又以四七并配五行。而其方位排置。略如天命图已例。则又似烦絮重复。恐不可施之于此图也。四七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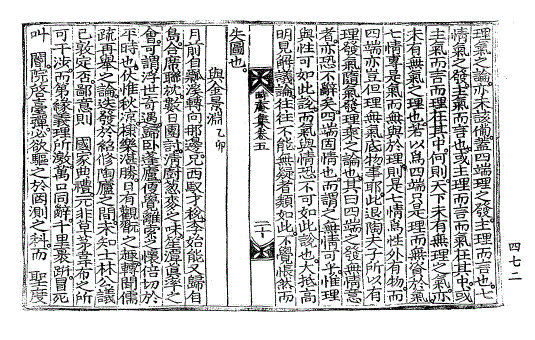 理气之论。亦未该备。盖四端理之发。主理而言也。七情气之发。主气而言也。或主理而言而气在其中。或主气而言而理在其中。何则。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也。若以为四端只是理而无资于气。七情专是气而无与于理。则是七情为性外有物。而四端亦岂但理无气底物事耶。此退陶夫子所以有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论也。其曰四端之发无情意者。亦恐不辞矣。四端固情也。而谓之无情可乎。惟理与性可如此说。而气与情恐不可如此说也。大抵高明见解议论。往往不能无疑者类如此。不觉怅然而失图也。
理气之论。亦未该备。盖四端理之发。主理而言也。七情气之发。主气而言也。或主理而言而气在其中。或主气而言而理在其中。何则。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也。若以为四端只是理而无资于气。七情专是气而无与于理。则是七情为性外有物。而四端亦岂但理无气底物事耶。此退陶夫子所以有理发气随气发理乘之论也。其曰四端之发无情意者。亦恐不辞矣。四端固情也。而谓之无情可乎。惟理与性可如此说。而气与情恐不可如此说也。大抵高明见解议论。往往不能无疑者类如此。不觉怅然而失图也。与(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答' 자로 되어 있다.)金景渊(乙卯)
月前自瓢溪转向那边。兄西驭才税。李始能又归自岛。合席联枕。数日团讨。清厨葱麦之味。笙潭真率之会。可谓浮世奇遇。归卧蓬庐。便觉离索之怀倍切于平时也。伏惟秋凉。棣樂湛胜。日有观玩之趣。转闻儒疏再举之论。迭发于绍修陶庐之间。未知士林公议已敦定否。鄙意则 国家典礼。元非草茅韦布之所可干涉。而第缘义理所激。万口同辞。千里裹趼。冒死叫 阍。院启台弹。必欲驱之于罔测之科。而 圣度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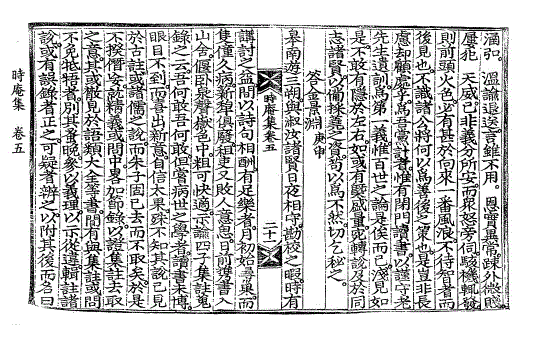 涵弘。 温谕退送。言虽不用。 恩实异常。疏外微贱。屡犯 天威。已非义分所安。而众怒旁伺。骇机辄发。则前头火色。必有甚于向来一番风浪。不待智者而后见也。不识诸公将何以为善后之策也。是岂非长虑却顾处乎。为吾党计者。惟有闭门读书。以谨守老先生遗训。为第一义。惟百世之论是俟而已。浅见如是。不敢有隐于左右。如或有槩盛量。宛转说及于同志诸贤。以备采荛之资。苟以为不然。切乞秘之。
涵弘。 温谕退送。言虽不用。 恩实异常。疏外微贱。屡犯 天威。已非义分所安。而众怒旁伺。骇机辄发。则前头火色。必有甚于向来一番风浪。不待智者而后见也。不识诸公将何以为善后之策也。是岂非长虑却顾处乎。为吾党计者。惟有闭门读书。以谨守老先生遗训。为第一义。惟百世之论是俟而已。浅见如是。不敢有隐于左右。如或有槩盛量。宛转说及于同志诸贤。以备采荛之资。苟以为不然。切乞秘之。答金景渊(庚申)
皋南游三朔。与淑汝诸贤日夜相守。勘校之暇。时有讲讨之益。间以诗句相酬。有足樂者。月初始寻巢。而只僮久病。薪犁俱废。租吏又败人意思。日前携书入山舍。偃卧泉声岳色中。粗可快适。示谕四子集注蒐录之云。吾何敢吾何敢。但尝病世之学者。读书未博。眼目不到。而喜出新意。自信太果。殊不知其说已见于古注或诸儒之说。而朱子固已去而不取矣。于是不揆僭妄。就精义或问中。略加节录。以證集注去取之意。其或散见于语类大全等书。间有与集注或问不免牴牾者。别其蚤晚。参以义理。以示从违。辑注诸说。或有误录者正之。可疑者辨之。以附其后而名曰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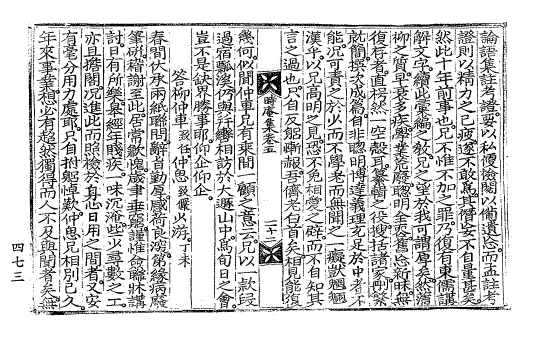 论语集注考證。要以私便检阅以备遗忘。而孟注考證则以精力之已疲。遂不敢为。其僭妄不自量甚矣。然此十年前事也。兄不惟不加之罪。乃复有东儒讲解文字。续此汇编之教。兄之望于我可谓厚矣。然蒲柳之质。早衰多疾。学业荒废。聪明全丧。旧忘新昧。无复存者。直枵然一空壳耳。纂辑之役。搜括诸家。删繁就简。撰次成篇。自非聪明博达义理充足于中者不能。况可责之于少而不学老而无闻之一痴呆魍魉汉乎。以兄高明之见。恐不免相爱之辟。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只自反躬惭赧。吾侪老白首矣。相见能复几何。似闻仲车兄有乘间一顾之意云。兄以一款段过宿瓢溪。仍与并辔相访于大遁山中。为旬日之会。岂不是缺界胜事耶。仰企仰企。
论语集注考證。要以私便检阅以备遗忘。而孟注考證则以精力之已疲。遂不敢为。其僭妄不自量甚矣。然此十年前事也。兄不惟不加之罪。乃复有东儒讲解文字。续此汇编之教。兄之望于我可谓厚矣。然蒲柳之质。早衰多疾。学业荒废。聪明全丧。旧忘新昧。无复存者。直枵然一空壳耳。纂辑之役。搜括诸家。删繁就简。撰次成篇。自非聪明博达义理充足于中者不能。况可责之于少而不学老而无闻之一痴呆魍魉汉乎。以兄高明之见。恐不免相爱之辟。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只自反躬惭赧。吾侪老白首矣。相见能复几何。似闻仲车兄有乘间一顾之意云。兄以一款段过宿瓢溪。仍与并辔相访于大遁山中。为旬日之会。岂不是缺界胜事耶。仰企仰企。答柳仲车(致任),仲思(致俨)少游。(丁未)
春间伏承两纸联问。辞旨勤厚。感荷良深。第缘病废笔研。稽谢至此。居常歉愧。岁聿垂穷。谨惟佥联床讲讨。日有所樂。皋经年贱疾。一味沉淹。些少寻数之工。亦且担阁。况进此而照检于身心日用之间者。又安有毫分用力处耶。只自拊躬悼叹。仲思兄相别已久。年来事业。想必有超然独得而人不及与闻者矣。无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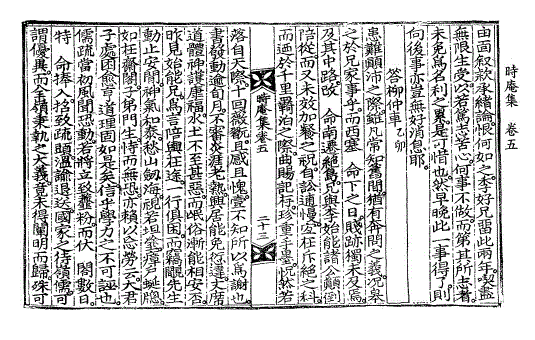 由面叙款承绪论。恨何如之。季好兄留此两年。吃尽无限生受。以若笃志苦心。何事不做。而第其所志者。未免为名利之累。是可惜也。然早晚此一事得了。则向后事亦岂无好消息耶。
由面叙款承绪论。恨何如之。季好兄留此两年。吃尽无限生受。以若笃志苦心。何事不做。而第其所志者。未免为名利之累。是可惜也。然早晚此一事得了。则向后事亦岂无好消息耶。答柳仲车(乙卯)
患难颠沛之际。虽凡常知旧间。犹有奔问之义。况皋之于兄家事乎。而西塞 命下之日。贱迹独未及焉。及其中路。改 命南迁绝岛。兄与李始能诸公颠倒陪从。而又未效加餐之祝。自讼逋慢。宜在斥绝之科。而乃于千里羁泊之际。曲赐记存。珍重手墨。恍然若落自天际。十回薇玩。且感且愧。壹不知所以为谢也。书发动逾旬月。不审炎涯老热。兴居能免愆违。丈席道体神护康福。水土不至甚恶。而氓俗渐能相安否。昨见始能兄。为言陪舆在途。一行俱困。而窃覸先生动止安閒。神气和泰。愁山剑海。视若坦涂。瘴户蜒窗。如在斋阁。子弟门生。恃而无恐。亦赖以忘劳云。大君子处困愈亨道理固如是矣。信乎学力之不可诬也。儒疏当初风闻恐动。若将立致齑粉。而伏 閤数日。特 命捧入。招致疏头。温谕退送。国家之待岭儒。可谓优异。而全岭秉执之大义。竟未得阐明而归。殊可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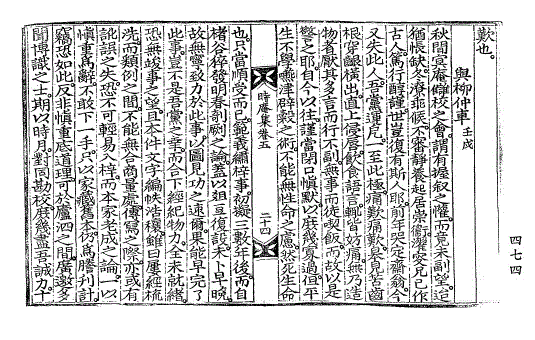 叹也。
叹也。与(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答' 자로 되어 있다.)柳仲车(壬戌)
秋间冥庵雠校之会。谓有握叙之欢。而竟未副望。迨犹怅缺。冬潦乖候。不审静养起居崇卫。濯叟兄已作古人。笃行醇谨。世岂复有斯人耶。前年哭定斋翁。今又失此人。吾党运厄。一至此极。痛叹痛叹。皋见苦齿根穿龈横出。直上侵唇。饮食语言。辄皆妨痛。无乃造物者厌其多言而行不副。无事而徒吃饭。而故以是警之耶。自今以往。谨当闭口慎默。以庶几寡过。但平生不学咽津辟谷之术。不能无性命之虑。然死生命也。只当顺受而已。范义绣梓事。初拟三数年后。而自楮谷猝发明春剞劂之论。盖以俎豆复设。未卜早晚。故无宁致力于此事。以图见功之速尔。果能早完了此事。岂不是吾党之幸。而合下经纪物力。全未就绪。恐无竣事之望。且本件文字编帙浩穰。虽曰屡经梳洗。而类例之间。不能无合商量处。传写之际。亦或有讹误之失。恐不可轻易入梓。而本家老成之论。一以慎重为辞。不敢下一手。只以家藏旧本。仍为誊刊计。窃恐如此。反非慎重底道理。可于庐泗之间。广邀多闻博识之士。期以时月。对同勘校。庶几尽吾诚力。十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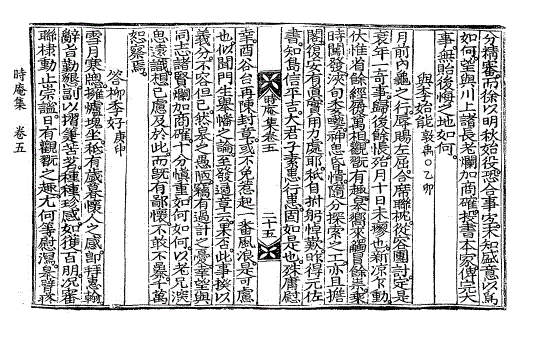 分精审。而徐以明秋始役。恐合事宜。未知盛意以为如何。望与川上诸长老烂加商确。投书本家。俾完大事。无贻后悔之地如何。
分精审。而徐以明秋始役。恐合事宜。未知盛意以为如何。望与川上诸长老烂加商确。投书本家。俾完大事。无贻后悔之地如何。与李始能(敦禹○乙卯)
月前内龟之行。辱赐左屈。合席联枕。从容团讨。定是衰年一奇事。归后馀怅。殆月十日未瘳也。新凉乍动。伏惟省馀经履万相。观玩有趣。皋向来触冒馀祟。乘时闯发。浃旬委呓。神思昏愦。随分探索之工。亦且担阁。复安有真实用力处耶。秖自拊躬悼叹。昨得元佐书。知岛信平吉。大君子素患行患。固如是也。殊庸慰幸。酉谷台再陈封章。或不免惹起一番风浪。是可虑也。似闻门生举幡之论。至发通章云。果否。此事揆以义分。不容但已。然皋之愚陋。窃有过计之忧。幸望与同志诸贤烂加商确。十分慎重。如何如何。以老兄深思远识。想已虑及于此。而既有鄙怀。不敢不㬥。千万恕察焉。
答柳季好(庚申)
雪月寒窗。拥炉块坐。秪有岁暮怀人之感。即拜惠翰。辞旨勤恳。副以摺箑苦茗。种种珍感。如获百朋。况审联棣动止崇谧。日有观玩之趣。尤何等慰泻。皋臂疼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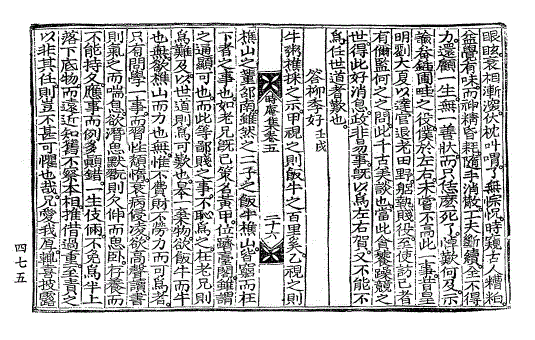 眼眩。衰相渐深。伏枕叫喟。了无悰恍。时窥古人糟粕。益觉有味。而神精昏耗。随手消散。工夫断续。全不得力。还顾一生。无一善状。而只恁么死了。悼叹何及。示谕畚锸圃畦之役。仆于左右。未尝不高此一事。昔皇明刘大夏以达官退老田野。躬执贱役。至使访己者有你监何之之问。此千古美谈也。当此贪饕躁竞之世。得此好消息。政非易事。既以为左右贺。又不能不为任世道者叹也。
眼眩。衰相渐深。伏枕叫喟。了无悰恍。时窥古人糟粕。益觉有味。而神精昏耗。随手消散。工夫断续。全不得力。还顾一生。无一善状。而只恁么死了。悼叹何及。示谕畚锸圃畦之役。仆于左右。未尝不高此一事。昔皇明刘大夏以达官退老田野。躬执贱役。至使访己者有你监何之之问。此千古美谈也。当此贪饕躁竞之世。得此好消息。政非易事。既以为左右贺。又不能不为任世道者叹也。答柳季好(壬戌)
牛粥樵采之示。甲视之则饭牛之百里奚。乙视之则樵山之董邵南。虽然之二子之饭牛樵山。皆穷而在下者之事也。如老兄既已策名黄甲。位跻台阁。虽谓之通显可也。而此等鄙贱之事。不耻为之。在老兄则为难及。以世道则为可叹也。皋一弃物。欲饭牛而牛也无。欲樵山而力也无。惟不费财不劳力而可为者。只有问学一事。而习性颓惰。衰病侵凌。欲高声读书则气乏而喘息。欲潜思默玩则欠伸而思卧。存养而不能持久。应事而例多颠错。一生伎俩。不免为半上落下底物。而远近知旧不察本相。推借过重。至责之以非其任。则岂不甚可惧也哉。兄爱我厚。辄喜披露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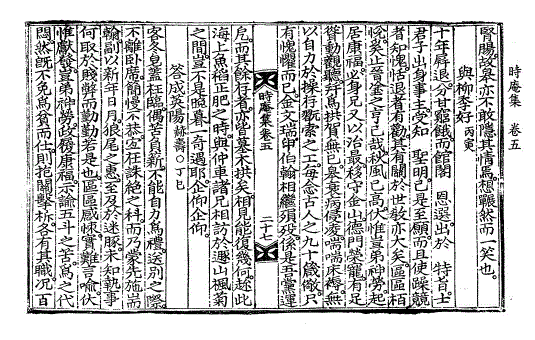 肾肠。故皋亦不敢隐其情焉。想冁然而一笑也。
肾肠。故皋亦不敢隐其情焉。想冁然而一笑也。与(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答' 자로 되어 있다.)柳季好(丙寅)
十年屏退。分甘穷饿。而馆阁 恩选。出于 特旨。士君子出身事主。受知 圣明。已是至愿。而且使躁竞者知愧。恬退者有劝。其有关于世教亦大矣。区区柏悦。奚止晋涂之亨已哉。秋风已高。伏惟岂弟神劳。起居康福。必身兄又以治最。移守金山。德门荣宠。有足耸动观听。并为拱贺无已。皋衰病侵凌。喘喘床褥。无以自力于操存玩索之工。每念古人之九十箴儆。只有愧惧而已。金文瑞,申伯翰相继殒殁。系是吾党运厄。而其馀存者。亦皆墓木拱矣。相见能复几何。趁此海上鱼稻正肥之时。与仲车诸兄相访于遁山枫菊之间。岂不是晚暮一奇遇耶。企仰企仰。
答成英阳(赫寿○丁巳)
客冬皂盖枉临。偶苦负薪。不能自力为礼。送别之际。不离卧席。简慢不恭。宜在诛绝之科。而乃蒙先施耑翰。副以新年日月。狼尾之惠。至及于迷豚。未知执事何取于贱弊而勤勤若是也。区区感悚。实难言喻。伏惟献发。岂弟神劳。政履康福。示谕五斗之苦。为之代闷。然既不免为贫而仕。则抱关击柝。各有其职。况百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6L 页
 里字牧之任乎。惟当随事尽力。要以无愧吾心而已。书尾所示。可谓相爱。而谓之相悉则恐未也。皋资性凡愚。最出人下。揣分量才。久绝当世之望矣。秖合读书善身。无负受中以生之责。是其本分事。而立志不固。因循颓惰。处心制行。动致愆尤。至今年踰五十。求为庸众人而且不可得矣。复岂有一毫名利之念。或萌于方寸中耶。俯赐阿豚诗。典雅可诵。但期许过重。恐非蒙呆者所敢承当。然使渠知解稍长。因此而或有激厉思齐之心。何莫非长者之赐乎。
里字牧之任乎。惟当随事尽力。要以无愧吾心而已。书尾所示。可谓相爱。而谓之相悉则恐未也。皋资性凡愚。最出人下。揣分量才。久绝当世之望矣。秖合读书善身。无负受中以生之责。是其本分事。而立志不固。因循颓惰。处心制行。动致愆尤。至今年踰五十。求为庸众人而且不可得矣。复岂有一毫名利之念。或萌于方寸中耶。俯赐阿豚诗。典雅可诵。但期许过重。恐非蒙呆者所敢承当。然使渠知解稍长。因此而或有激厉思齐之心。何莫非长者之赐乎。答金真宝(周教○乙卯)
五载邻壤。既饱仁声。半夜旅灯。款承绪论。犁然相契。几乎忘形。皋平常读古书。遇有会心人。虽百世之远。便起执鞭之思。今何幸得见执事于人人之中。其钦慕之笃。又岂止寂寥卷中人比哉。归伏穷庐。第觉离索之苦。较切于前日愿识之怀耳。新年华翰。忽伴梅信而至。百回薇玩。清香津津然袭人矣。感荷之至。如获百朋。仍审献发。仕学俱优。神相康福。所留册子。重违勤教。黾俛舍置。而久尘清案。殊甚非便。幸望从近还掷。而如蒙不外。指示疵颣。或赐斤正。又何惠如之。又有元日小诗。忘拙写呈。一笑之馀。敢望琼报。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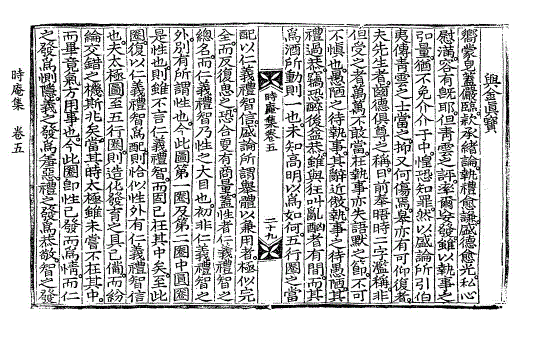 与(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答' 자로 되어 있다.)金真宝
与(저본의 원목차에는 '答' 자로 되어 있다.)金真宝向蒙皂盖俨临。款承绪论。执礼愈谦。盛德愈光。私心慰满。容有既耶。但青云之评。率尔妄发。虽以执事之弘量。犹不免介介于中。惶恐知罪。然以盛论所引伯夷传青云之士当之。抑又何伤焉。皋亦有可仰复者。夫先生者。齿德俱尊之称。日前奉晤时二字滥称。非但受之者万万不敢当。在执事亦失语默之节。不可不慎也。愚陋之待执事。其辞近傲。执事之待愚陋。其礼过恭。窃恐醉后益恭。虽与狂叫乱酗者有间。而其为酒所动则一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五行圈之当配以仁义礼智信。盛论所谓举体以兼用者。极似完全。而反复思之。恐合更有商量。盖性者仁义礼智之总名。而仁义礼智乃性之大目也。初非仁义礼智之外。别有所谓性也。今此图第一圈及第二圈中圆圈是性也。则虽不言仁义礼智。而固已在其中矣。至此圈。复以仁义礼智为配。则恰似性外有仁义礼智信也。夫太极图至五行圈。则造化发育之具已备。而纷纶交错之机斯兆矣。当其时太极虽未尝不在其中。而毕竟气方用事也。今此圈即性已发而为情。而仁之发为恻隐。义之发为羞恶。礼之发为恭敬。智之发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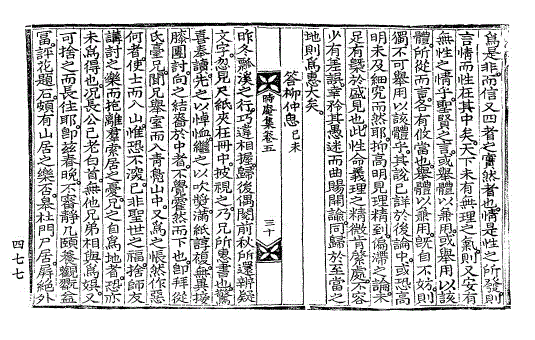 为是非。而信又四者之实然者也。情是性之所发。则言情而性在其中矣。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则又安有无性之情乎。圣贤之言。或举体以兼用。或举用以该体。所从而言。各有攸当也。举体以兼用。既自不妨。则独不可举用以该体乎。其说已详于后论中。或恐高明未及细究而然耶。抑高明见理精到。偏滞之论。未足有槩于盛见也。此性命义理之精微肯綮处。不容少有差误。幸矜其愚迷而曲赐开谕。同归于至当之地则为惠大矣。
为是非。而信又四者之实然者也。情是性之所发。则言情而性在其中矣。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则又安有无性之情乎。圣贤之言。或举体以兼用。或举用以该体。所从而言。各有攸当也。举体以兼用。既自不妨。则独不可举用以该体乎。其说已详于后论中。或恐高明未及细究而然耶。抑高明见理精到。偏滞之论。未足有槩于盛见也。此性命义理之精微肯綮处。不容少有差误。幸矜其愚迷而曲赐开谕。同归于至当之地则为惠大矣。答柳仲思(己未)
昨冬瓢溪之行。巧违相握。归后偶阅前秋所还辨疑文字。忽见尺纸夹在册中。披视之。乃兄所惠书也。惊喜奉读。先之以悼恤。继之以吹奖。满纸谆复。无异接膝团讨。向之结啬于中者。不觉霍然而下也。即拜从氏台兄。闻兄举室而入青凫山中。又为之怅然作恶何者。使士而入山。惟恐不深。已非圣世之福。舍师友讲讨之樂而抱离群索居之忧。兄之自为地者。恐亦未为得也。况长公已老白首。无他兄弟相与为娱。又可舍之而长往耶。即玆春晚。不审静几颐养观玩益富。评花题石。颇有山居之樂否。皋杜门尸居。屏绝外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8H 页
 事。时抽乱帙。分寸看读。而神精耗散。收拾不上。只有日暮途远之叹耳。仁说汇编。承已成书。可见真实用工处。恨未及奉玩。虽未知规模条例之如何。然朱子尝以类聚言仁。为不免长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其为后世虑远矣。窃尝妄谓人患不为仁耳。苟欲为仁。不过从事于孔子所告颜渊,仲弓,樊迟者而实用力焉尔。如欲博求乎仁之体用形状名义意味及用工节度。则晦斋求仁录备矣。尝见权厚庵明诚录。类聚洛闽言仁诸说。妄以为此已末矣。夫程朱论仁。固所以发明孔孟之旨。然朱子尝以类聚孔孟言仁。虑有后弊。况后人又聚诸说。以资口耳之习。恐非朱子之所与也。兄之所编。虽曰用意精深。未必无补于学者。无乃或近于架叠之嫌而有违于朱子之意耶。妄恃相爱。发此狂僭。未知盛意以为如何。
事。时抽乱帙。分寸看读。而神精耗散。收拾不上。只有日暮途远之叹耳。仁说汇编。承已成书。可见真实用工处。恨未及奉玩。虽未知规模条例之如何。然朱子尝以类聚言仁。为不免长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其为后世虑远矣。窃尝妄谓人患不为仁耳。苟欲为仁。不过从事于孔子所告颜渊,仲弓,樊迟者而实用力焉尔。如欲博求乎仁之体用形状名义意味及用工节度。则晦斋求仁录备矣。尝见权厚庵明诚录。类聚洛闽言仁诸说。妄以为此已末矣。夫程朱论仁。固所以发明孔孟之旨。然朱子尝以类聚孔孟言仁。虑有后弊。况后人又聚诸说。以资口耳之习。恐非朱子之所与也。兄之所编。虽曰用意精深。未必无补于学者。无乃或近于架叠之嫌而有违于朱子之意耶。妄恃相爱。发此狂僭。未知盛意以为如何。答柳仲思(丁卯)
皋积祸召殃。哭妻哭妇。悼割之怀。已难形喻。而父子相守。冷淡家计。有如老头陀活契。命也。只得任之而已。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近始收召残魂。为分寸填补之计。而断续无常。随手消散。加以宿苦视疾。近又闯发。寻常浇灌之工。亦且担阁。馀日几何。只自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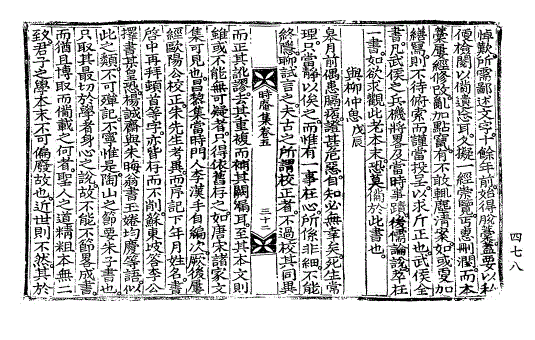 悼叹。所需鄙述文字。十馀年前。始得脱稿。盖要以私便检阅以备遗忘耳。久拟一经崇览。丐惠删润。而本稿屡经修改。乱加点窜。有不敢辄尘清案。如或更加缮写。则不待俯索而谨当投呈。以求斤正也。武侯全书。凡武侯之兵机将略及当时事迹。后儒论说。萃在一书。如欲求观此老本末。恐莫备于此书也。
悼叹。所需鄙述文字。十馀年前。始得脱稿。盖要以私便检阅以备遗忘耳。久拟一经崇览。丐惠删润。而本稿屡经修改。乱加点窜。有不敢辄尘清案。如或更加缮写。则不待俯索而谨当投呈。以求斤正也。武侯全书。凡武侯之兵机将略及当时事迹。后儒论说。萃在一书。如欲求观此老本末。恐莫备于此书也。与柳仲思(戊辰)
皋月前偶患膈痞。證甚危恶。自知必无幸矣。死生常理。只当静以俟之。而惟有一事在心。所系非细。不能终隐。聊试言之。夫古之所谓校正者。不过校其同异而正其讹谬。去其重复而补其阙漏耳。至其本文则虽或不能无可疑者。只得依旧存之。如唐宋诸家文集可见也。昌黎集当时门人李汉手自编次。厥后屡经欧阳公校正。朱先生考异。而序记下年月姓名。书启中再拜顿首等字。亦皆存而不削。苏东坡答李公择书某皇恐。杨诚斋与朱晦翁书玉婘均庆等语。似此之类。不可殚记。不宁惟是。陶山之节要朱子书也。只取其最切于学者身心之说。故不能不节略成书。而犹且博取而备载之何者。圣人之道精粗本无二致。君子之学本末不可偏废故也。近世则不然。其于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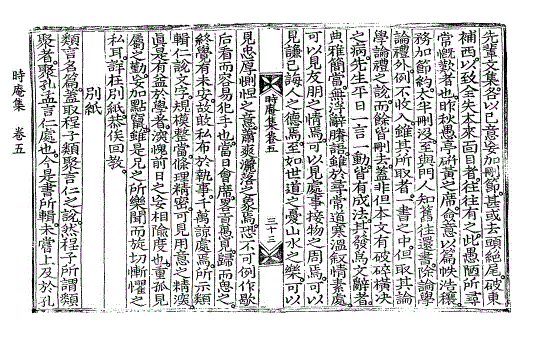 先辈文集。各以己意妄加删节。甚或去头绝尾。破东补西。以致全失本来面目者。往往有之。此愚陋所寻常慨叹者也。昨秋愚亭研黄之席。佥意以篇帙浩穰。务加节约。太半删没。至与门人知旧往还书。除论学论礼外。例不收入。虽其所取者。一书之中。但取其论学论礼之说。而馀皆删去。盖非但本文有破碎横决之病。先生平日一言一动。皆有成法。其发为文辞者。典雅简当。无浮辞剩语。虽于寻常道寒温叙情素处。可以见友朋之情焉。可以见处事接物之周焉。可以见谦己诲人之德焉。至如世道之忧山水之樂。可以见忠厚恻怛之意。萧爽洒落之象焉。恐不可例作歇后看而容易犯手也。当日会席。略贡愚见。归而思之。终觉有未安。故敢私布于执事。千万谅处焉。所示类辑仁说文字。规模整当。条理精密。可见用意之精深。真是有益于学者。深愧前日之妄相隃度也。重孤见属之勤。妄加点窜。虽是兄之所樂闻而旋切惭惧之私耳。详在别纸。恭俟回教。
先辈文集。各以己意妄加删节。甚或去头绝尾。破东补西。以致全失本来面目者。往往有之。此愚陋所寻常慨叹者也。昨秋愚亭研黄之席。佥意以篇帙浩穰。务加节约。太半删没。至与门人知旧往还书。除论学论礼外。例不收入。虽其所取者。一书之中。但取其论学论礼之说。而馀皆删去。盖非但本文有破碎横决之病。先生平日一言一动。皆有成法。其发为文辞者。典雅简当。无浮辞剩语。虽于寻常道寒温叙情素处。可以见友朋之情焉。可以见处事接物之周焉。可以见谦己诲人之德焉。至如世道之忧山水之樂。可以见忠厚恻怛之意。萧爽洒落之象焉。恐不可例作歇后看而容易犯手也。当日会席。略贡愚见。归而思之。终觉有未安。故敢私布于执事。千万谅处焉。所示类辑仁说文字。规模整当。条理精密。可见用意之精深。真是有益于学者。深愧前日之妄相隃度也。重孤见属之勤。妄加点窜。虽是兄之所樂闻而旋切惭惧之私耳。详在别纸。恭俟回教。别纸
类言名篇。盖取程子类聚言仁之说。然程子所谓类聚者。聚孔孟言仁处也。今是书所辑。未尝上及于孔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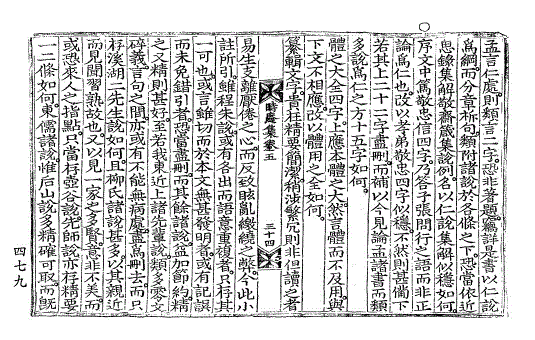 孟言仁处。则类言二字。恐非著题。窃详是书以仁说为纲。而分章析句。类附诸说于各条之下。恐当依近思录集解敬斋箴集说例。名以仁说集解似稳如何。
孟言仁处。则类言二字。恐非著题。窃详是书以仁说为纲。而分章析句。类附诸说于各条之下。恐当依近思录集解敬斋箴集说例。名以仁说集解似稳如何。序文中笃敬忠信四字。乃答子张问行之语而非正论为仁也。改以孝弟敬忠四字似稳。不然则甚备下若其上二十二字尽删。而补以今见论孟诸书而类多说为仁之方十五字如何。
体之大全四字。上应本体之大。然言体而不及用。与下文不相应。改以体用之全如何。
纂辑文字。贵在精要简洁。稍涉繁冗则非但读之者易生支离厌倦之心。而反致眩乱缴绕之弊。今此小注所引。虽程朱说。或有各出而语意重复者。只存其一可也。或言虽切而于本文无甚发明者。或有记误而未免错引者。恐当尽删。而其馀诸说。益加节约。精之又精则甚好。至若我东近上诸先辈说。类多零文碎义。言句之间。亦或有不能无病处。尽为删去。而只存溪湖二先生说如何。且柳氏诸说甚多。以其亲近而见闻习熟故也。又以见一家之多贤。意非不美。而或恐来人之指点。只当存壶谷说。先师说亦存精要一二条如何。东儒诸说。惟后山说多精确可取。而既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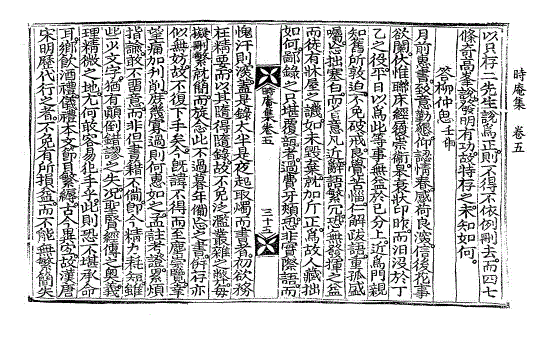 以只存二先生说为正。则不得不依例删去。而四七条奇高峰说。发明有功。故特存之。未知如何。
以只存二先生说为正。则不得不依例删去。而四七条奇高峰说。发明有功。故特存之。未知如何。答柳仲思(壬申)
月前惠书。致意勤恳。仰认情眷。感荷良深。信后花事欲阑。伏惟联床经履崇卫。皋衰状印昨。而汩没于丁乙之役。平日以为此等事无益于己分上。近为门亲知旧所敦迫。不免破戒。良觉苦恼。仁解跋语。重孤盛嘱。忘拙塞白。而旨意凡近。辞语繁冗。恐无发挥之益而徒有床屋之讥。如未毁弃。就加斤正。为故人藏拙如何。鄙录之只堪覆瓿者。过费牙颊。恐非实际语。而愧汗则深。盖是录太半是夜起取烛而书者。初欲务在精要。而以其随得随录。故不免泛滥丛杂之弊。每拟删繁就简。而旋念此不过暮年备忘之书。并存亦似无妨。故不复下手矣。今既讳不得而至尘崇览。幸望痛加刊削。庶几寡过则何惠如之。孟注考證。累烦指谕。敢不留意。而非但书籍不备。即今精力耗短。虽些少文字。犹有颠倒错谬之失。况圣贤经传之奥。义理精微之地。尤何敢容易犯手乎。此则恐不堪承命耳。乡饮酒礼。仪礼本文节目繁缛。古今异宜。故汉唐宋明历代行之者。不免有所损益。而不能无繁简失
时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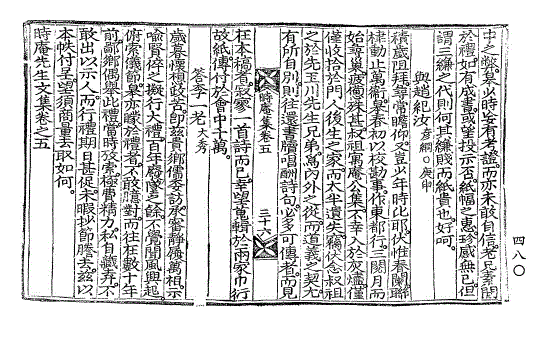 中之弊。皋少时妄有考證。而亦未敢自信。老兄素閒于礼。如有成书。或望投示否。纸幅之惠。珍感无已。但谓三缣之代则何其缣贱而纸贵也。好呵。
中之弊。皋少时妄有考證。而亦未敢自信。老兄素閒于礼。如有成书。或望投示否。纸幅之惠。珍感无已。但谓三缣之代则何其缣贱而纸贵也。好呵。与赵纪汝(彦纲○庚申)
积岁阻拜。寻常瞻仰。又岂少年时比耶。伏惟春阑。联棣动止万卫。皋春初以校勘事。作东都行。三阅月而始寻巢。疲惫殊甚。叔祖寓庵公集。不幸入于灰烬。仅仅收拾于门人后生之家。而太半遗失。窃伏念叔祖之于先玉川先生兄弟。为内外之从。而道义之契。尤有所自别。则往还书牍唱酬诗句。必多可传者。而见在本稿者。寂寥一首诗而已。幸望蒐辑于两家巾衍故纸。传付于会中千万。
答李一老(大秀)
岁暮怀想政苦。即玆贵乡儒委访。承审静履万相。示喻贤倅之拟行大礼。百年废坠之馀。不觉闻风兴起。俯索仪节。皋亦矇于礼者。不敢臆对。而往在数十年前。鄙乡偶举此礼。当时考索。极费精力。私自藏弆。不敢出以示人。而行礼期日甚促。未暇抄节誊去。玆以本帙付呈。望须商量去取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