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亭集卷之七 第 x 页
晦亭集卷之七
论
论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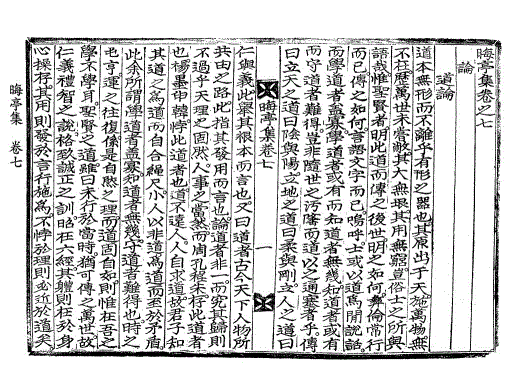 道论
道论道本无形而不离乎有形之器也。其原出于天。施万物。无不在。历万世未尝敝。其大无垠。其用无穷。岂俗士之所与语哉。惟圣贤者。明此道而传之后世。明之如何。彝伦常行而已。传之如何。言语文字而已。呜呼。士或以道为閒说话。而学道者盖寡。学道者或有而知道者无几。知道者或有而守道者难得。岂非随世之污隆而道以之通塞者乎。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举其根本而言也。又曰道者古今天下人物所共由之路。此指其发用而言也。论道者非一。而究其归则不过乎天理之固然。人事之当然。而周孔程朱。存此道者也。杨墨申韩。悖此道者也。道不远人。人自求道。故君子知其道之为道而自合绳尺。小人以非道为道而至于矛盾。此余所谓学道者盖寡。知道者无几。守道者难得也。时之屯亨。运之往复。系是自然之理。而道固自如。则惟在吾之学不学耳。圣贤之道。虽曰未行于当时。犹可传之万世。故仁义礼智之说。格致诚正之训。昭在六经。其体则在于身心操存。其用则发于言行施为。不悖于理则必近于道矣。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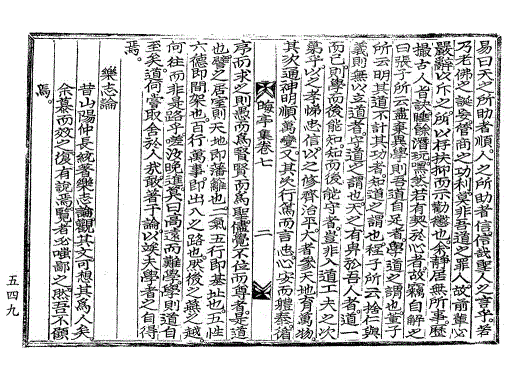 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信哉圣人之言乎。若乃老佛之诞妄。管商之功利。莫非吾道之罪人。故前辈必严辞以斥之。所以存扶抑而示劝惩也。余静居无所事。历撮古人旨诀。睡馀潜玩。嘿然若有契于心者。故窃自解之曰张子所云尽弃异学则吾道自足者。学道之谓也。董子所云明其道不计其功者。知道之谓也。程子所云舍仁与义则无以立道者。守道之谓也。天之有畁于吾人者。道一而已。则学而后能知。知而后能守者。岂非入道工夫之次第乎。以之孝悌忠信。以之修齐治平。大者参天地育万物。其次通神明顺万变。又其次行笃而言忠。心安而体泰。循序而求之则愚而为贤贤而为圣。尽觉不位而尊者。是道也。譬之居室则天地即藩篱也。二气五行即基址也。五性六德即间架也。百行万事。即出入之路也。然后之燕之越。何往而非是路乎。嗟汝晚进。莫曰高远而难学。学则道自至矣。道何尝取舍于人哉。敢著于论。以俟夫学者之自得焉。
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信哉圣人之言乎。若乃老佛之诞妄。管商之功利。莫非吾道之罪人。故前辈必严辞以斥之。所以存扶抑而示劝惩也。余静居无所事。历撮古人旨诀。睡馀潜玩。嘿然若有契于心者。故窃自解之曰张子所云尽弃异学则吾道自足者。学道之谓也。董子所云明其道不计其功者。知道之谓也。程子所云舍仁与义则无以立道者。守道之谓也。天之有畁于吾人者。道一而已。则学而后能知。知而后能守者。岂非入道工夫之次第乎。以之孝悌忠信。以之修齐治平。大者参天地育万物。其次通神明顺万变。又其次行笃而言忠。心安而体泰。循序而求之则愚而为贤贤而为圣。尽觉不位而尊者。是道也。譬之居室则天地即藩篱也。二气五行即基址也。五性六德即间架也。百行万事。即出入之路也。然后之燕之越。何往而非是路乎。嗟汝晚进。莫曰高远而难学。学则道自至矣。道何尝取舍于人哉。敢著于论。以俟夫学者之自得焉。乐志论
昔山阳仲长统著乐志论。观其文。可想其为人矣。余慕而效之。复有说焉。览者必嗤鄙之。然吾不顾焉。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0H 页
 人之生而为丈夫身于天地间者何限。其功名事业而各有命焉。岂智力之所可逆料耶。惟志也吾所自任而自行者。为士者其肯规规于外物而不思所以乐吾志乎。余世家隐农。薄田可以供菽水。晚筑山庄小亭。可以便起居。于分自知已足矣。况又所性也厌闻雌黄。所守也自持淡素。一生措置。无求于人。而惟听命于天矣。静居无事。自然兴到。则飘然独往于山深水丽之地。听鸟而看花。归卧幽栖。或曳杖彷徨于松篁梧柳之下。筑土而种石。农桑渔樵。问于溪童巷老。嘉言善行。考诸圣经贤传。俯仰今古。无思无虑。夜久月明则大读董生行一篇。继以诵五柳先生传数篇。已而笑而自语于心曰此可为丈夫之事业乎。视世之奔汩于风尘者。毕竟所得何如哉。笑矣乎。
人之生而为丈夫身于天地间者何限。其功名事业而各有命焉。岂智力之所可逆料耶。惟志也吾所自任而自行者。为士者其肯规规于外物而不思所以乐吾志乎。余世家隐农。薄田可以供菽水。晚筑山庄小亭。可以便起居。于分自知已足矣。况又所性也厌闻雌黄。所守也自持淡素。一生措置。无求于人。而惟听命于天矣。静居无事。自然兴到。则飘然独往于山深水丽之地。听鸟而看花。归卧幽栖。或曳杖彷徨于松篁梧柳之下。筑土而种石。农桑渔樵。问于溪童巷老。嘉言善行。考诸圣经贤传。俯仰今古。无思无虑。夜久月明则大读董生行一篇。继以诵五柳先生传数篇。已而笑而自语于心曰此可为丈夫之事业乎。视世之奔汩于风尘者。毕竟所得何如哉。笑矣乎。晦亭集卷之七
说
心性情说
夫人得天地之衷而为一身之主。性者心之体而寂然不动。其蕴也有仁义礼智之德。情者心之用而感而遂通。其发也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是以心统性情而其蕴也均善无恶者。理所固然。而其发也不无善恶者。气之使然矣。虞典之人心道心。因发而异名。邹传之人性物性。以类而各正。惟其情之为情。即朱夫子所谓随感而见者也。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0L 页
 人物理气说
人物理气说大抵理气之原。自太极阴阳。而理有常而无形。气无常而有形。是以人物之生。莫不有理气之相资。所以生者理也。所以生之者气也。然则理无无气之理。气无无理之气。此所谓不相离不相杂者也。然或单言理或兼言气。或推本原而言之。或从流行而言之。若言先后次第则一阴一阳。生生不穷。其理则未尝不先具。栗谷尤庵两先生之论甚多。而其中最为明白者有一二条。玆表而出之。
栗谷曰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气有为而理无为。故气发而理乘之。又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
尤庵曰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而言者。有从流行而言者。盖谓理气混瀜无间。而理自理气自气。又未尝夹杂。故其言理有动静者。从理之主气而言也。其言理无动静者。从气之运理而言也。其言有先后者。从理气源头而言也。其言无先后者。从理气流行而言也。
栗谷又曰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情是感物所发底。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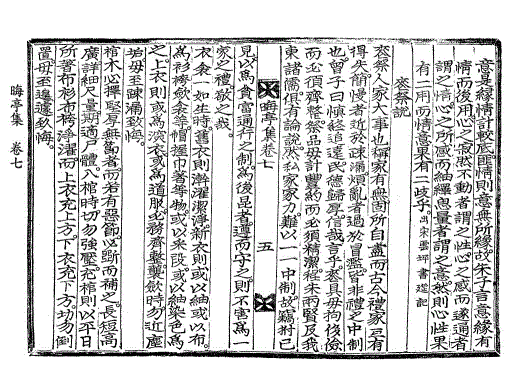 意是缘情计较底。匪情则意无所缘。故朱子言意缘有情而后用。心之寂然不动者谓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谓之情。心之所感而䌷绎思量者谓之意。然则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出宋云坪书筵记。)
意是缘情计较底。匪情则意无所缘。故朱子言意缘有情而后用。心之寂然不动者谓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谓之情。心之所感而䌷绎思量者谓之意。然则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出宋云坪书筵记。)丧祭说
丧祭人家大事也。称家有无。固所自尽。而古今礼家互有得失。简慢者近于疏漏。烦乱者过于冒滥。皆非礼之中制也。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信哉言乎。丧具毋拘侈俭而必须齐整。祭品毋计丰约而必须精洁。程朱两贤及我东诸儒。俱有论说。然私家家力。难以一一中制。故窃拊己见。以为贫富通行之制。为后昆者。遵而守之。则不害为一家之礼。敬之哉。
衣衾一如生时。旧衣则浣濯洁净。新衣则或以䌷或以布。为衫裤敛衾等。帽握巾著等物。或以采段。或以䌷染色为之。上衣则或为深衣。或为道服。必务齐整。袭敛时。勿近尘垢。毋至疏漏致悔。
棺木必择坚厚无节者。而若有恶节。必斲而补之。长短高广。详细尺量。期适尸体。入棺时。切勿强压。充棺则以平日所著布衫布裤净濯。而上衣充上方。下衣充下方。切勿倒置。毋至遑遽致悔。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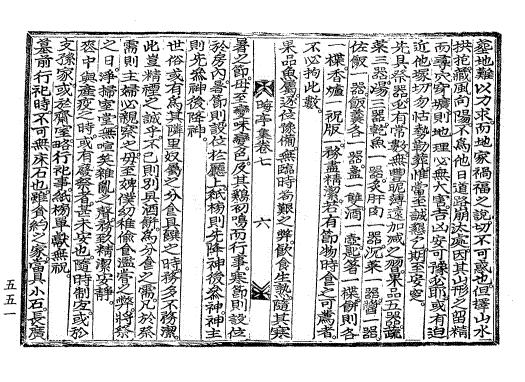 葬地难以力求。而地家祸福之说。切不可惑也。但择山水拱抱。藏风向阳。不为他日道路崩汰处。因其山形之留精而寻穴穿圹。则地理必无大害。吉凶安可豫必耶。或有迫近他冢。切勿怙势勒葬。惟当至诚恳乞。期至安窆。
葬地难以力求。而地家祸福之说。切不可惑也。但择山水拱抱。藏风向阳。不为他日道路崩汰处。因其山形之留精而寻穴穿圹。则地理必无大害。吉凶安可豫必耶。或有迫近他冢。切勿怙势勒葬。惟当至诚恳乞。期至安窆。先具祭器。必有常数。无丰昵薄远加减之习。果品五器。蔬菜三器。汤三器。乾鱼一器。炙肝肉一器。沉菜一器。酱一器。佐饭一器。饭羹各一器。盏一双。酒一壶。匙箸一楪。饼则各一楪。香炉一祝版一。务尽精洁。若有节物时食之可荐者。不必拘此数。
果品鱼属。逐位豫备。无临时苟艰之弊。饮食生熟。随其寒暑之节。毋至变味变色。及其鸡初鸣而行事。寒节则设位于房内。暑节则设位于厅上。纸榜则先降神后参神。神主则先参神后降神。
世俗或有为其邻里奴属之分食具馔之时。务多不务洁。此岂精禋之诚乎。不已则别具酒饼。为分食之需。凡于祭需则主妇必亲察之。毋至婢仆幼稚偷食滥尝之弊。将祭之日。净扫室堂。无喧笑杂乱之声。务致精洁安静。
丧中与产疫之时。或有废祭者。甚未安也。随时制宜。或于支孙家。或于斋室。略行祀事。纸榜单献无祝。
墓前行祀时。不可无床石也。虽贫约之家。当具小石。长广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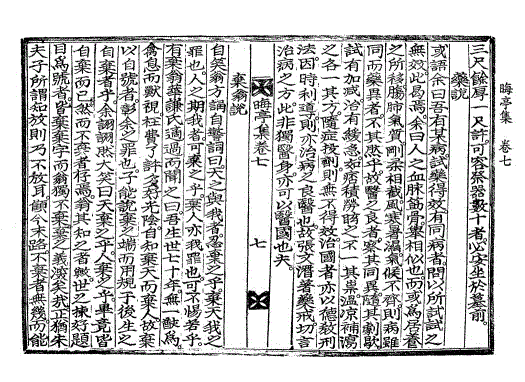 三尺馀厚一尺许。可容祭器数十者。必安坐于墓前。
三尺馀厚一尺许。可容祭器数十者。必安坐于墓前。药说
或语余曰吾有某病。试药得效。有同病者。问以所试试之无效。此曷焉。余曰人之血脉筋骨。举相似也。而或为居养之所移。肠肺气质。刚柔相截。风寒暑湿。气候不齐。则病虽同而药异者。不其然乎。故医之良者。察其同异。随其剧歇。试有加减。治有缓急。如痞积劳眩之不一其祟。温凉补泻之各一其方。随症投剂。则无不得效。治国者亦以德教刑法。因时利导。则亦治病之良医也。故张文潜著药戒。切言治病之方。此非独医身。亦可以医国也夫。
弃翁说
自笑翁方诵自警词曰。天之与我者。忍弃之乎。弃天我之罪也。人之期我者。可弃之乎。弃人亦我罪也。可不惕若乎。有弃翁华谦氏适过而闻之曰。吾生世七十年。无一猷为。禽息而兽视。枉费了许多好光阴。自知弃天而弃人。故弃以自号者。彰余之罪也。子能说弃之端而用规于后生之自弃者乎。余诩诩然大笑曰天弃之乎。人弃之乎。毕竟皆自弃而已。然而不弃者存焉。翁其知之者欤。世之拣好题目为号者。皆弃弃字而翁独不弃。弃之义深矣哉。正犹朱夫子所谓知放则乃不放耳。顾今末路。不弃者无几。而能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2L 页
 自知其弃者有几人哉。翁既自知。则其所以不弃之者。自在其中矣。翁之弃。足以为世人自谓不弃者戒。噫。
自知其弃者有几人哉。翁既自知。则其所以不弃之者。自在其中矣。翁之弃。足以为世人自谓不弃者戒。噫。莲沼说
周茂叔爱莲说曰莲。花之君子也。噫历观古今莲之爱。惟周茂叔一人。其后闻茂叔之风者。往往种莲而爱之。其皆君子之徒欤。余未敢知也。然苟使其人君子也。其所爱之花。虽非莲亦不害为君子。奚特莲哉。余素有花癖。名其所居曰花溪。今春适与族人章赫游。年才十八。其人可佳。一日问其志之所乐。曰吾将凿沼种莲。观鱼其上。亦足养吾之性焉。无他志也。余闻而嘉之。作莲沼说。
晦亭集卷之七
杂著
浴沂楼讲义
讲长曰心性理气之说。为吾儒格致之大头段也。心之寂感。性之偏全。理之显微。气之粹驳。皆大体说。而究其筑底处。则心性非二致。理气非二体也。讲生曰然则从上圣贤。胡为曰心曰性曰理曰气而分作四物耶。曰心者性之统体。性者心之条理。而言其本体则理也。言其运用则气也。于其间。有内外精粗本末先后。故分开处各指所主。合一处并探其原也。对曰先儒所云性则理心则气者。亦似牵合四物为二物何欤。讲长曰在人物为性。在天地为理。而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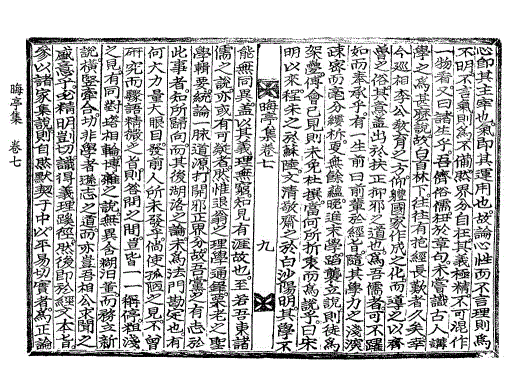 心即其主宰也。气即其运用也。故论心性而不言理则为不明。不言气则为不备。然界分自在。其义极精。不可混作一物看。又曰诸生乎。吾侪俗儒。狃于章句。未尝识古人讲学之为甚么说。故白首林下。往往有抱经长叹者久矣。幸今巡相李公教育之方。仰体国家作成之化。而导之以齐鲁之俗。其意盖出于扶正抑邪之道也。为吾儒者。可不跃如而奉承乎。有一生前曰前辈于经旨。随其学力之浅深疏密而毫分缕析。更无馀蕴。晚进末学。蹈袭立说。则徒为架叠。傅会己见则未免杜撰。当何所折衷而为说乎。曰宋明以来。程朱之于苏陆。文清敬斋之于白沙阳明。其学不能无同异。盖以其义理无穷。知见有涯故也。至若吾东诸儒之说。亦或有可疑者。然惟退翁之理学通录。栗老之圣学辑要。统论一脉道源。打开邪正界分。故吾党之有志于此事者。知所归向。而其后湖洛之论。未为法门勘定也。有何大力量大眼目。发前人所未发乎。倘使孤陋之见。不曾研究而骤语精微之旨。则答问之间。岂皆一一称停。粗浅之见。有同对塔相轮。博杂之说。无异含糊汩董。而务立新说。横竖牵合。切非学者逊志之道。而亦岂吾相公求闻之盛意乎。必精明剀切。识得义理蹊径。然后即于经文本旨。参以诸家集说。则自然默契于中。以平易切实者。为正论
心即其主宰也。气即其运用也。故论心性而不言理则为不明。不言气则为不备。然界分自在。其义极精。不可混作一物看。又曰诸生乎。吾侪俗儒。狃于章句。未尝识古人讲学之为甚么说。故白首林下。往往有抱经长叹者久矣。幸今巡相李公教育之方。仰体国家作成之化。而导之以齐鲁之俗。其意盖出于扶正抑邪之道也。为吾儒者。可不跃如而奉承乎。有一生前曰前辈于经旨。随其学力之浅深疏密而毫分缕析。更无馀蕴。晚进末学。蹈袭立说。则徒为架叠。傅会己见则未免杜撰。当何所折衷而为说乎。曰宋明以来。程朱之于苏陆。文清敬斋之于白沙阳明。其学不能无同异。盖以其义理无穷。知见有涯故也。至若吾东诸儒之说。亦或有可疑者。然惟退翁之理学通录。栗老之圣学辑要。统论一脉道源。打开邪正界分。故吾党之有志于此事者。知所归向。而其后湖洛之论。未为法门勘定也。有何大力量大眼目。发前人所未发乎。倘使孤陋之见。不曾研究而骤语精微之旨。则答问之间。岂皆一一称停。粗浅之见。有同对塔相轮。博杂之说。无异含糊汩董。而务立新说。横竖牵合。切非学者逊志之道。而亦岂吾相公求闻之盛意乎。必精明剀切。识得义理蹊径。然后即于经文本旨。参以诸家集说。则自然默契于中。以平易切实者。为正论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3L 页
 而考据焉。以巧奇浮诞者。为邪论而取舍焉。则不为私主所蔽。而似免架叠之嫌杜撰之失也。吾非知学者。而所闻于师友者。不过如此。未知诸生之意。果以为然否耶。念乎哉。
而考据焉。以巧奇浮诞者。为邪论而取舍焉。则不为私主所蔽。而似免架叠之嫌杜撰之失也。吾非知学者。而所闻于师友者。不过如此。未知诸生之意。果以为然否耶。念乎哉。思辨录(并序)
余少业功令。未尝识学问之为甚么事。于焉岁不我与。恰踰无闻之年。每中夜蹶起。不觉歔欷者也。尝观栗谷先生之言曰科业理学。两无所成。则老大之后。虽悔曷追。此真吾今日画帖也。噫幼而学者。壮而欲行之。天爵修则人爵必自至。此非后世设科取人之谓。乃贤能宾兴之道也。是故古之儒者。学优则仕。秪患无学。不患无仕矣。胡乃俗渐渝薄。汉唐以来。词赋以取材。于是词章之徒。专尚藻华。不复知有德行之科。此造士之失其道者耳。然古来儒贤。类多阐发于科目中。得君行道。展布所学。如宋之程朱两夫子。尤其杰然于千古者。而我东则自圃老至退栗诸先生。俱是备道德兼体用者也。然则学问科业。不可分两截看。而今之学者。常以学问为高远之事。惟科业是事。判为两涂。岂非没知觉之大者乎。大抵学问。非别件物也。乃日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4H 页
 用事耳。自一身一家。至天下万事。莫不有当行之路是也。馀力学文。以治科业。而时之屈伸。数之屯亨。都付于自家之天分。而不为外胶之所摇夺。则学问科业。两无害于心术。所患者惟恐吾之立志之不笃耳。惟我 国家。昔在中叶。名硕辈出。磨砻诱掖。可谓家君子户贤人。此实圣人作成之化。而世道有升降。末路靡靡。所谓儒者。寥寥无闻者久矣。抑有之而未之闻欤。呜呼。文者载道之器也。圣贤千言万语。无物不论。无事不究。粲然载之于六经四子。毫分缕析。更无馀蕴。此实昏衢指南也。晚进后学。但当深体而力行之。何用论说架叠于其间哉。余晚居茅山。静玩书史。周程张朱。耳提而面命之。退栗尤春。难疑而答问之。朝暮相遇。不患无师。然懦昏成痼。役于走作。对卷则似得领会。临事而茫无体验。如是玩愒。终无究竟。则将不知为何物人也。断当变化吾气质。改图吾心志然后。庶可窥见其入道之万一。而所恨者无左右资益。未知归宿。故抄出前贤绪馀。窃附己论。以为慎思明辨之一助云。
用事耳。自一身一家。至天下万事。莫不有当行之路是也。馀力学文。以治科业。而时之屈伸。数之屯亨。都付于自家之天分。而不为外胶之所摇夺。则学问科业。两无害于心术。所患者惟恐吾之立志之不笃耳。惟我 国家。昔在中叶。名硕辈出。磨砻诱掖。可谓家君子户贤人。此实圣人作成之化。而世道有升降。末路靡靡。所谓儒者。寥寥无闻者久矣。抑有之而未之闻欤。呜呼。文者载道之器也。圣贤千言万语。无物不论。无事不究。粲然载之于六经四子。毫分缕析。更无馀蕴。此实昏衢指南也。晚进后学。但当深体而力行之。何用论说架叠于其间哉。余晚居茅山。静玩书史。周程张朱。耳提而面命之。退栗尤春。难疑而答问之。朝暮相遇。不患无师。然懦昏成痼。役于走作。对卷则似得领会。临事而茫无体验。如是玩愒。终无究竟。则将不知为何物人也。断当变化吾气质。改图吾心志然后。庶可窥见其入道之万一。而所恨者无左右资益。未知归宿。故抄出前贤绪馀。窃附己论。以为慎思明辨之一助云。大凡人性本善。而差失则恶矣。古语云愿天常生善人。愿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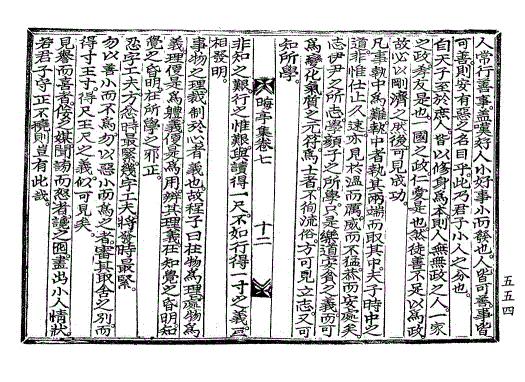 人常行善事。盖叹好人小好事小而发也。人皆可善。事皆可善。则安有恶之名目乎。此乃君子小人之分也。
人常行善事。盖叹好人小好事小而发也。人皆可善。事皆可善。则安有恶之名目乎。此乃君子小人之分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则人无无政之人。一家之政。孝友是也。一国之政。仁爱是也。然徒善不足以为政。故必以刚济之然后。可见成功。
凡事执中为难。执中者执其两端而取其中。夫子时中之道。非惟仕止久速。亦见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处矣。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只是乐道安贫之义。而可为变化气质之元符。为士者。不徇流俗。方可见立志。又可知所学。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与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之义。互相发明。
事物之理。裁制于心者义也。故程子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理便是为体。义便是为用。辨其理义。在知觉之昏明。知觉之昏明。在所学之邪正。
忍字工夫。方忿时最紧。几字工夫。将发时最紧。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者。审其取舍之别。而得寸王寸。得尺王尺之义。似可见矣。
见誉而喜者。佞之媒。闻谤而怒者。谗之囮。画出小人情状。若君子守正不挠则岂有此哉。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5H 页
 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君子反身修省。惟尽在我之道而已。
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君子反身修省。惟尽在我之道而已。事之是者为理。则心之正者非道乎。
人有卓然之行。则訾毁必随。然岂可恶訾毁而不为卓行乎。
克复之工。非勇则不能。存省之工。非智则不能。
施为欲作千匀(从金)弩。磨砺当如百鍊金二句。当为轻动妄行者之佩服也。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两语。当为逸居无教者之鉴戒也。
人之心神。昼则为耳目所牵。游散在外。夜则专一在内。故静坐工夫。自夜气中流出来。
心有人心道心之别。性有天命气质之分。治心养性之道。必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焉。天命之性。须用存养工夫。气质之性。须用省察工夫。
道在外德在内。行于外而得于内。故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又曰修德而凝道。此合内外之道也。
学者于心性理气之说。见先辈旨论。虽有嘿会于心。不即于事物上体验则非格致之工也。须著某物看曰此心也。此性也。此理也。此气也。昭然分晓然后。可期成己成物之功。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5L 页
 性情思虑志意皆统于心
性情思虑志意皆统于心元在天为德之全体。而亨利贞用也。仁在人为心之全体。而义礼智用也。
存心之德。莫先于求仁。穷物之理。莫先于养知。制事之方。莫先于义。果行之实。莫先于勇。敬则通贯四者。而一生受用不尽者也。
继志述事。谓之达孝。则忠君悌长。夫妇别朋友信。亦皆父母之志事也。可不继述乎。此所以孝为百行之源者也。
韩魏公曰父母慈而子孝。常事不足称。惟不慈而不失孝。乃为可称。是知父母则孰不止慈。而为子者罕见其孝。如此之人。魏公之罪人也。
孔子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吕东莱曰惧者福之原。忽者祸之门。张文潜曰物不受变则材不成。人不涉难则智不明。此皆恐惧戒慎动心忍性之道也。可不念哉。
衣冠。摄威仪养性情之具。不可华侈。亦不可粗率。
杨墨之近乎仁义。如乡愿之近乎德。而实则德之贼也。
人或有以技术而言预知祸福。避凶趍吉。此特技之末也。苟知积善有庆。积恶有殃。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之道。则岂非避凶趍吉之大法乎。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6H 页
 朱子曰欲矫好名之弊。则必至廉隅亏损。学者于此等事。更加省察。
朱子曰欲矫好名之弊。则必至廉隅亏损。学者于此等事。更加省察。士为士业。农为农业。不可妄议政之得失。人之长短。民俗如此则岂不美哉。
静里乾坤大。閒中日月长二句。穷三才洞万物之意。自然包得。使人肩耸。
五常之信。犹五行之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四端之中。四时不言土而土在四时之季。则可见人道之协于天道。
利有利己利物之殊。利己之利。小人之心也。利物之利。君子之心也。
夫子罕言利者。为救时人趋利之弊也。曾传末章有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邹论首篇亦曰何必曰利。亦惟仁义而已。曾孟之言。发明夫子罕言之意也。
欲利于己则必至于害人。故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人于财上。必以利义。辨其取舍。然后似无悖入悖出之患矣。
汉儒之学。尽出于章句之专门。而惟董子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语。廓扫功利之说。而创出道义之论。此所以为西京真儒。而亦可谓一言为天下后世法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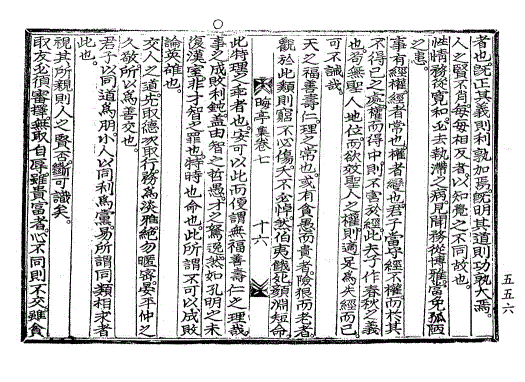 者也。既正其义则利孰加焉。既明其道则功孰大焉。
者也。既正其义则利孰加焉。既明其道则功孰大焉。人之贤不肖。每每相反者。以知觉之不同故也。
性情务从宽和。必去执滞之病。见闻务从博雅。当免孤陋之患。
事有经权。经者常也。权者变也。君子当守经不权。而于其不得已之处。权而得中。则不害于经。此夫子作春秋之义也。苟无圣人地位。而欲效圣人之权。则适足为失经而已。可不诫哉。
天之福善寿仁。理之常也。或有贪愚而贵者。险狠而老者。观于此类则穷不必伤。夭不必悼。然伯夷饿死。颜渊短命。此特理之乖者也。安可以此而便谓无福善寿仁之理哉。
事之成败利钝。盖由智之哲愚。才之驽逸。然如孔明之未复汉室。非才智之罪也。特时也命也。此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也。
交人之道。先取德次取行。务为淡雅。绝勿昵密。晏平仲之久敬。所以为善交也。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党。易所谓同类相求者此也。
视其所亲则人之贤否。断可识矣。
取友必须审择。无取自辱。虽贵富者。心不同则不交。虽贫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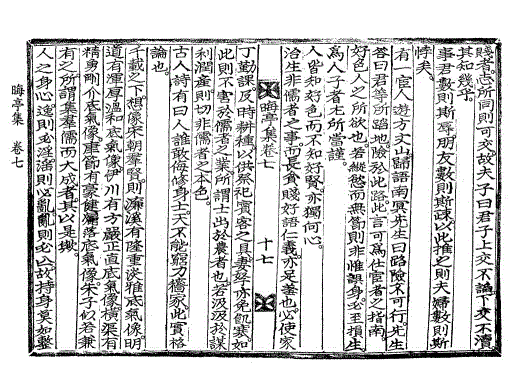 贱者。志所同则可交。故夫子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贱者。志所同则可交。故夫子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事君数则斯辱。朋友数则斯疏。以此推之则夫妇数则斯悖矣。
有一宦人游方丈山。归语南冥先生曰路险不可行。先生答曰君等所蹈地。险于此路。此言可为仕宦者之指南。
好色人之所欲也。若纵欲而无节则非惟误身。必至损生。为人子者尤所当谨。
人皆知好色而不知好贤。亦独何心。
治生非儒者之事。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必使家丁勤课。及时耕种。以供祭祀宾客之具。妻孥亦免饥寒。如此则不害于儒者之业。所谓士出于农者也。若汲汲于谋利润产。则切非儒者之本色。
古人诗有曰人谁敢侮修身士。天不能穷力穑家。此实格论也。
千载之下。想像宋朝群贤。则濂溪有隆重淡雅底气像。明道有运厚温和底气像。伊川有方严正直底气像。横渠有精勇刚介底气像。康节有豪健洒落底气像。朱子似若兼有之。所谓集群儒而大成者。其以是欤。
人之身心。逸则必淫。淫则必乱。乱则必亡。故持身莫如整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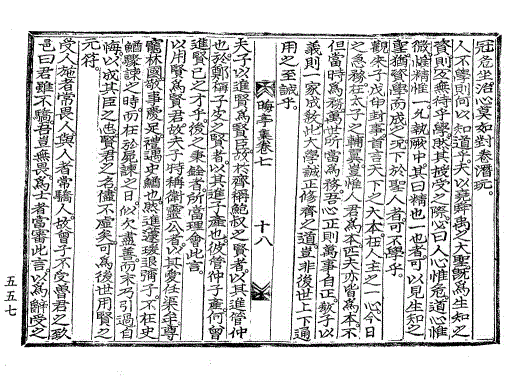 冠危坐。治心莫如对卷潜玩。
冠危坐。治心莫如对卷潜玩。人不学则何以知道乎。夫以尧舜禹之大圣。既为生知之资。则宜无待乎学。然其授受之际。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曰精也一也者。可以见生知之圣。犹资学而成之。况下于圣人者。可不学乎。
观朱子戊申封事。首言天下之大本。在人主之一心。今日之急务。在太子之辅翼。岂惟人君为本。匹夫亦皆为本。不但当时为务。万世所当为务。吾心正则万事自正。教子以义则一家成教。此大学诚正修齐之道。岂非后世上下通用之至诫乎。
夫子以进贤为贤臣。故于齐称鲍叔之贤者。以其进管仲也。于郑称子皮之贤者。以其进子产也。彼管仲子产。何曾进贤己之才乎。后之秉铨者。所当理会此言。
以用贤为贤君。故夫子特称卫灵公者。以其爱任渠牟。尊宠林国。敬事庆足。礼遇史䲡也。然进蘧瑗退弥子。不在史䲡骤谏之时。而在于尸谏之日。似欠尽善。而末乃引过自悔。以成其臣之忠。贤君之名。尽不虚矣。可为后世用贤之元符。
受人施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故曾子不受鲁君之致邑曰君虽不骄。吾岂无畏。为士者当审此言。以为辞受之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8H 页
 法可也。
法可也。夫子曰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盖言利害得丧之间。见君子小人之别也。黔娄之不戚戚不汲汲。程子之富不淫贫亦乐。皆得夫子之此旨也。
见高崖而知颠坠之患。临巨涛而知风波之患者。夫子畏匡困陈而发此深省也。自古体仁义道德者。莫如夫子。而尚罹此患。抑子渊所谓道大莫能容于天下者非耶。后之贤人君子。𨓏𨓏不免于世俗之恶者。无足怪矣。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则君子可不慎其所与处乎。
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此皆不顺其治而穷尽其力之害也。曷不危哉。所当念者。
诗之教温厚而失则愚。书之教疏通而失则诬。礼之教恭敬而失则烦。乐之教广博而失则奢。易之教精微而失则害。春秋之教。属辞比事而失则乱。学者可不存省而体察乎。
农夫之田土地。而其所稼穑。谷种而已。圣人之田人情也。礼以耕之。义以种之。学以耨之。乐以播之。仁以聚之。其利与农夫何如哉。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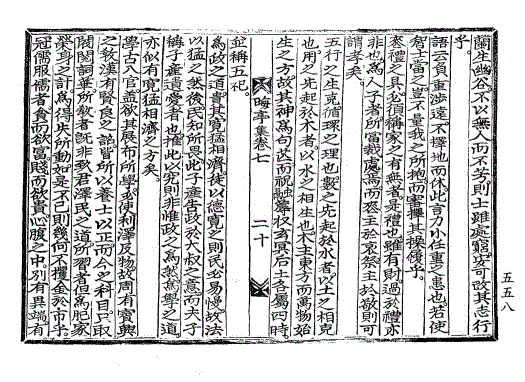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则士虽处穷。安可改其志行乎。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则士虽处穷。安可改其志行乎。语云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此言力小任重之患也。若使智士当之。岂不量我之所抱。而审择其操履乎。
丧礼之具。必须称家之有无者。是礼也。虽有财。过于礼亦非也。为人子者。所当裁处焉。而丧主于哀。祭主于敬则可谓孝矣。
五行之生克。循环之理也。数之先起于水者。以土之相克也。用之先起于木者。以水之相生也。木主东方而万物始生之方。故其神为句芒。而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各属四时。并称五祀。
为政之道。贵其宽猛相济。徒以德宽之则民必易慢。故法以猛之然后。民知所畏。此子产告政于大叔之意。而夫子称子产遗爱者也。推此以究则非惟政之为然。为学之道。亦似有宽猛相济之方矣。
学古入官。盖欲其展布所学。必使利泽及物。故周有賨兴之教。汉有贤良之诏。皆所以养士以正。而今之科目。只取阀阅词华。所教者既非致君泽民之道。所习者但为肥家荣身之计。为得失所动。如是不已则几何不攫金于市乎。冠儒服儒者。贫而欲富。贱而欲贵。心腹之中。别有异端。有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9H 页
 甚于杨墨老佛。此莫非养不以正而溺于流俗之弊也。何异斨根而求茂。汩源而索清乎。良可悲夫。
甚于杨墨老佛。此莫非养不以正而溺于流俗之弊也。何异斨根而求茂。汩源而索清乎。良可悲夫。文之有易诗书春秋。与道之有皇王帝霸。
诗变而骚。骚变而辞。可见风气之渐降也。
冠昏之礼。所以示敬。丧祭之礼。所以兴孝。朝聘之礼。所以示忠。饮飨之礼。所以明义。此皆天理之节文而人事之仪则也。圣人之教。岂不至广而且远乎。
君有争臣。父有争子。兄有争弟。士有争友。则国无危亡。家无悖乱。此皆忠言逆耳而利于行之验也。
曾点沂雩之对。悠然得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底意想。故喻之以尧舜气像。此特一时之言。脱却事物。偶合圣意故耳。然千载之下。想像当时光景。则不言之前。鼓瑟希三字。已包得狂狷志趣。后人所谓含言意于未对。露气像于将乱者。善形容点也之样子也。呜呼。恨不生于邹鲁。抠衣侍坐。一论所志矣。
否泰往复。天地之理。而所谓造物无全功者也。时之穷亨盛衰。事之利害得丧。无非自然。士当随其所遭。安义处命。不可忘分纵欲。而一生需用者。惟有一道。大易所谓谦之道而已。书谦六爻于坐侧。常目而服膺焉。
贤才之见用于世。自古难矣。𨓏𨓏有认燕石为玉。指赵璧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59L 页
 为璞者。此亦气数也。若使识鉴通明之人。观人于平日无事之时。则可知患难时措办矣。其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贪禄爵而轻名义者。必是逃难偷生之人也。其有刚毅之态。谠直之论。轻爵禄而扶纲纪者。必是伏节死义之人也。故朱子曰无事之日。得死义之士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伏节死义之事。而惟其所恃以安宁于平日者矣。岂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待之耶。此言岂非取人之龟鉴乎。
为璞者。此亦气数也。若使识鉴通明之人。观人于平日无事之时。则可知患难时措办矣。其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贪禄爵而轻名义者。必是逃难偷生之人也。其有刚毅之态。谠直之论。轻爵禄而扶纲纪者。必是伏节死义之人也。故朱子曰无事之日。得死义之士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伏节死义之事。而惟其所恃以安宁于平日者矣。岂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待之耶。此言岂非取人之龟鉴乎。古有三至之化。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士悦。至乐无声而民和。此三代之隆也。生于此世者。其乐何如哉。易所谓士生大有之时。缊袍华于佩玉。饮水甘于列鼎者也。
古语云忧治世而危明主。此益之戒舜曰儆戒无虞。伊尹之戒太甲曰无安厥位之意也。然则忧乱世危昏主。为如何哉。是以圣贤有终身之忧危。
物之利者。害必随之。事之喜者。伤必随之。当兢惕者。
明人何景明诗曰多情自古还多恨。此可谓画景绝唱。
饮食所以民生日用而养吾口体者也。只令免饥而已。若役于口腹。贪饕厌饫。则疾病之所由生而人亦贱之。所谓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0H 页
 甘脆肥脓。腐肠之药也。至于曲蘖。非惟伐性。或至丧身。
甘脆肥脓。腐肠之药也。至于曲蘖。非惟伐性。或至丧身。范希文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忧者易豫卦之义也。后乐者易谦卦之道也。若希文者。亦可谓用易之君子。而又于枕上卧计当日之事与食。则岂不为诗所谓不素餐之君子乎。今之谓士者。不知忧乐之所当。而揔未免食浮于实。哀哉。
心者天之所以赋于人而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世间甚事孰非心字中做出乎。颜渊之心斋。其旨深矣。
世间人事。皆由懦怠二字坏了。懦是无用之谓也。怠是不勤之谓也。苟有立志不懦。用力不怠。则甚事做不得。非勇无以行。非勤无所得。曷不惕若。
公正刚明四个字。反复䌷绎。则私之反为公。邪之反为正。柔之对为刚。昏之对为明。公以心言。正以道言。刚以行言。明以知言。公则正矣。刚则明矣。凡人之一言一动。天下之万物万事。罔非此四者之功用。故礼著三无私。诗垂思无邪。书有柔克之训。易有用晦之象。学者所当书壁而深玩。
人之忧乐。所以害心术也。虽忧忧不可剧。虽乐乐不可极。事有大体。又有委曲。当随处措宜。而苟无先见之知。必生后悔。苟无远虑之量。必生近患。
事之非常者变也。处之非经者权也。当其常而守其经。圣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0L 页
 凡皆可能也。至于遭变而行权。不失其正者。惟圣贤为能。而非众人之所可及也。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盖言其权之难。而夷齐季札之徒。所以轻千乘之富而求一心之所安也。朱子之发此言于便殿奏劄。既有所指。而亦可为守经行权之格论也。
凡皆可能也。至于遭变而行权。不失其正者。惟圣贤为能。而非众人之所可及也。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盖言其权之难。而夷齐季札之徒。所以轻千乘之富而求一心之所安也。朱子之发此言于便殿奏劄。既有所指。而亦可为守经行权之格论也。由之果。赐之达。求之艺。夫子既许其各有所长。可使从政。程子曰人皆有所长。取其长。皆可用也。然则人无无用之人。而物无无用之物也。
处事之际。有利害有是非。主于利害则见物而不见理。主于是非则见理而不见物。
假义之人。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好名之人。或能让富贵于明显之地。而未免较得失于微细之间。如此者。皆非真情之发也。故观人不于其所勉处。于其所忽处然后。可知其所安之实也。学者于此。不可顷刻不察也。
孟子曰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国恒亡。此在上者之所鉴也。又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达。此在下者之所鉴也。
世或以一言盖一人。一事盖一时。盖非与人不求备之道也。常借馀地。第观归宿处如何耳。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1H 页
 人之教导之方。必自孩提有识之时。故贾生之言曰太子生而使正士傅之则习于礼乐。罔非其正。故三代之所以善治也。使恶人师之则习于刑法。尽是其恶。故秦之所以短祚也。贾生此言。盖亦幼子常视毋诳之义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当以此为教子弟之前鉴。岂其善恶之性。初有别也。特以教导有邪正之分也。
人之教导之方。必自孩提有识之时。故贾生之言曰太子生而使正士傅之则习于礼乐。罔非其正。故三代之所以善治也。使恶人师之则习于刑法。尽是其恶。故秦之所以短祚也。贾生此言。盖亦幼子常视毋诳之义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当以此为教子弟之前鉴。岂其善恶之性。初有别也。特以教导有邪正之分也。邪正之分。惟在公私义利之间。在我无格致诚正之学。则疑似之际。真赝莫辨。巧言谄辞。谓之格论。忠言谠论。谓之诽谤。是以君子。贵穷理而大居敬。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故贾生之言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学者当谨礼而畏法。见其将然已然之如何耳。
奢与俭。皆失中。然俭非恶行。故夫子曰与其奢也宁俭。若俭之过则至于吝啬近利之归。为士者当折中焉。
春秋鲁史之旧名。而夫子加春于建子之月。则非惟奉天时尊正朔也。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
忠恕之说。窃意明道就人分上分别浅深而言。伊川就道理上该贯上下而言。明道之言。一见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贤愚皆获其益。伊川之言。乍见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不能识其味。于此亦可见矣。明道浑然天成。不犯人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1L 页
 力故也。伊川功夫造极。可夺天巧故也。
力故也。伊川功夫造极。可夺天巧故也。朱子答张敬夫论仁曰今之学者。厌烦就简。避远求捷。此风已盛。趋于险薄。若更如此导之则益长其计获欲速之心。而愈见促迫纷扰。反陷于不仁。一字见解之差。其弊至于此。学术之不可不审也有如是夫。
论人而丧实妄也。蔽美妒也。必也不言其所短。只言其所长。则可谓尚德之一助矣。何可轻易是非乎。
君子之行。自当顾义理之是非。以为从违。不当视同列之喜怒。以为前却也。
后人论前人之事。而有可疑处。则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
心经一书。首揭大禹谟人心道心。篇终附之以朱夫子尊德性铭。心学之要。当先识危微之分。故以人心道心。开示学者。精择固守之方。而至于存养之地则不过持敬工夫。故终之以尊德性铭。
退陶老先生引胡文定语而告人曰。人之出处语嘿。如寒温饥饱。自知斟酌。不可决之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若文定退溪则学问通明。知觉精详。不待人教导而自合绳尺。然下此之人。凡于事物言行。不欲资问指教而肆行己见。终至偾败。则其悔如何。退翁此言。以自家一时措处言也。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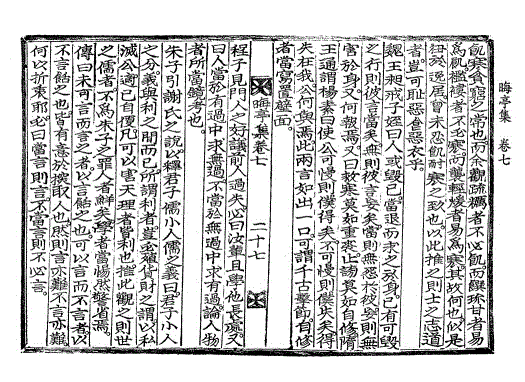 饥寒贫穷之常也。而余观疏粝者不必饥。而馔珍甘者易为饥。褴褛者不必寒。而袭轻煖者易为寒。其故何也。似是狃于逸居。曾未忍饥耐寒之致也。以此推之则士之志道者。岂可耻恶食恶衣乎。
饥寒贫穷之常也。而余观疏粝者不必饥。而馔珍甘者易为饥。褴褛者不必寒。而袭轻煖者易为寒。其故何也。似是狃于逸居。曾未忍饥耐寒之致也。以此推之则士之志道者。岂可耻恶食恶衣乎。魏王昶戒子侄曰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无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报焉。又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隋王通谓杨素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我。公何与焉。此两言如出一口。可谓千古击节。自修者当写置壁面。
程子见门人之好议前人过失。必曰汝辈且学他长处。又曰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论人物者所当镜考也。
朱子引谢氏之说。以释君子儒小人儒之义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推此观之则世之儒者。不为朱子之罪人者鲜矣。学者当惕然警省焉。
传曰未可言而言之者。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者。以不言餂之也。皆有意于探取人也。然则言亦难不言亦难。何以折衷耶。必曰当言则言。不当言则不必言。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2L 页
 传曰均善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是以朱子曰教人者随其人之高下而告语。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故圣人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笃焉。何可强其所未能及者耶。
传曰均善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是以朱子曰教人者随其人之高下而告语。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故圣人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笃焉。何可强其所未能及者耶。春秋圣人之书。其于曲直邪正之辨。至严至密。一毫不放过。犹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臣子之讳君亲固也。至于贤者而犹讳之何也。盖贤者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细行微有所可议处。不可以小而伤大也。此言婉曲。学者当玩索焉。
游头流录
日玉洞老人卢锡龙。执丈馀杖。踵门访余。余时午睡方浓。撞地高唱曰昼寝何故。惊起迎之。既就席。置杖于坐侧。甚爱护焉。其大不满半握。重不过一斤。皮骨斑斑成文。若著钉妆饬然。举以坠诸地则硁硁有金铁之鸣焉。余拊之曰此何木耶。山梨也。梨之为木。罕睹其直且长者。如是丛薄穷山。不为樵苏之所侵斫而转入于老人之手。物之遇幸矣。而抑有可叹者。若使佚宕游散之少年。扶而陟崇冈涉长湖。则凌千里遍八域。无限名胜。可以踏阅。乃今所见者不出渭南剡中耶。惜乎其不遇主也杖兮。老人勃然曰吾年七十二。粤自杖乡。出入相须者此物也。居则同坐。起则
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3H 页
 并行。鸟雀之害谷。挥而逐之。行旅之问程。举而指之。田有水倚听焉。郡有令扶往焉。体疲步倦则两手据其端。叉腰而伸之。或遇穷溪断涧可涉不可涉处。则任余身而侧仗作气。发声勇超一二丈许。老年快事。何加于此。自以为与物相得。死生同归。遽反以广搜远历。欲责其功。甚矣子之好怪也。余作而谢曰学圣人者。岂不思不语怪之训。素好奇古。𨓏𨓏忤俗。无怪其目之以好怪也。夫人之遇不遇。早晚异焉。物之用不用。久近别焉。贵贱贤不肖。老则固杖之。杖则必未久。故即物感怀。发此不遇主之叹。非谓其不遇于物也。自古杖之有功者。葛坡之化龙。丛林之解虎。圯桥丹藜。花溪桃竹。至若糜生芦丁公藤。皆已见称于世。以山梨为杖者。今始见之。好怪孰甚于此。况齿洽望八。迹不出百里之外。可知其无劳于杖。而固非杖之不欲劳于人也。遽将一枕青山。长卧不起。则是杖也与谁奚适。见今衰谢犹刚康。虽难远历。近有方丈。方丈三神之一也。𨓏𨓏有游仙者。其中又有不死药云。幸及此时。扶而陟之。采其药而寿斯民。则物与我皆无尽藏也。杖之功岂小哉。毋使不遇于其主。无称于后也。老人辗然良久。嫣然笑曰诺。余遂折九节竹杖之。联筇而南行。岁己酉闰四月十七日也。午后过德泉。将向旧沙村。行数里越场岘。舍直路由小径而右。
并行。鸟雀之害谷。挥而逐之。行旅之问程。举而指之。田有水倚听焉。郡有令扶往焉。体疲步倦则两手据其端。叉腰而伸之。或遇穷溪断涧可涉不可涉处。则任余身而侧仗作气。发声勇超一二丈许。老年快事。何加于此。自以为与物相得。死生同归。遽反以广搜远历。欲责其功。甚矣子之好怪也。余作而谢曰学圣人者。岂不思不语怪之训。素好奇古。𨓏𨓏忤俗。无怪其目之以好怪也。夫人之遇不遇。早晚异焉。物之用不用。久近别焉。贵贱贤不肖。老则固杖之。杖则必未久。故即物感怀。发此不遇主之叹。非谓其不遇于物也。自古杖之有功者。葛坡之化龙。丛林之解虎。圯桥丹藜。花溪桃竹。至若糜生芦丁公藤。皆已见称于世。以山梨为杖者。今始见之。好怪孰甚于此。况齿洽望八。迹不出百里之外。可知其无劳于杖。而固非杖之不欲劳于人也。遽将一枕青山。长卧不起。则是杖也与谁奚适。见今衰谢犹刚康。虽难远历。近有方丈。方丈三神之一也。𨓏𨓏有游仙者。其中又有不死药云。幸及此时。扶而陟之。采其药而寿斯民。则物与我皆无尽藏也。杖之功岂小哉。毋使不遇于其主。无称于后也。老人辗然良久。嫣然笑曰诺。余遂折九节竹杖之。联筇而南行。岁己酉闰四月十七日也。午后过德泉。将向旧沙村。行数里越场岘。舍直路由小径而右。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3L 页
 一樵夫问曰未知何处居两班。欲向那边。必从此径。登降极艰。宜从左。余曰知我为游山客足矣。何必问居住向方。樵夫曰吾恐其失路。故敢有问焉。且谚曰知路问行。请无怪之。指小丛石间曰此有泉。极清冽不渴。手掬饮之。好哉好哉。曰瓢以饮之可也。而忘了未偕矣。子教以掬饮之。倘先会得耶。樵夫笑曰偶发适中也。遂涤掬饮之。果味好。谓老人曰试饮之。饮之曰恨不便作酒也。曰酒客见水常恋酒。所谓因物情迁者也。相与噱噱。举杖叉腰。行吟招隐操一遍。过中垈村。一脊山脚。欲走反蹲。上有草茵。遂坐爇烟草。有童男女三人驱牛下来。可知日之夕矣。起而环脊抵墓所拜省。向山直家。其老母出迎曰儿也俄出猎矣。倘获一雉。可以供餐。有顷荷铳而返。无获矣。老人叹曰食指不动。非主之过。客之数空矣。进夕饭。辞以无餐。见卵汁一器甚浓脆。余笑曰鸡卵甘软。不下于山鸡也。夕后出户踞岩上。时山月隐隐。草鸟相应。凝然得山中意味。夜分乃寝。粤八日向向阳洞。山直子年才八九。挟册而前。汝何去。将学于吴先生。知其为义之氏也。随童而访焉。林间一草亭。新搆甚开朗。小坐向春萝台。义之弹冠而出。又有朴生者偕焉。至外台上。呼酒劝老人。杯行到余。余曰未也。借老人饮之。又饮之。其酣适之味。不下于自饮也。入内台中。见壁面
一樵夫问曰未知何处居两班。欲向那边。必从此径。登降极艰。宜从左。余曰知我为游山客足矣。何必问居住向方。樵夫曰吾恐其失路。故敢有问焉。且谚曰知路问行。请无怪之。指小丛石间曰此有泉。极清冽不渴。手掬饮之。好哉好哉。曰瓢以饮之可也。而忘了未偕矣。子教以掬饮之。倘先会得耶。樵夫笑曰偶发适中也。遂涤掬饮之。果味好。谓老人曰试饮之。饮之曰恨不便作酒也。曰酒客见水常恋酒。所谓因物情迁者也。相与噱噱。举杖叉腰。行吟招隐操一遍。过中垈村。一脊山脚。欲走反蹲。上有草茵。遂坐爇烟草。有童男女三人驱牛下来。可知日之夕矣。起而环脊抵墓所拜省。向山直家。其老母出迎曰儿也俄出猎矣。倘获一雉。可以供餐。有顷荷铳而返。无获矣。老人叹曰食指不动。非主之过。客之数空矣。进夕饭。辞以无餐。见卵汁一器甚浓脆。余笑曰鸡卵甘软。不下于山鸡也。夕后出户踞岩上。时山月隐隐。草鸟相应。凝然得山中意味。夜分乃寝。粤八日向向阳洞。山直子年才八九。挟册而前。汝何去。将学于吴先生。知其为义之氏也。随童而访焉。林间一草亭。新搆甚开朗。小坐向春萝台。义之弹冠而出。又有朴生者偕焉。至外台上。呼酒劝老人。杯行到余。余曰未也。借老人饮之。又饮之。其酣适之味。不下于自饮也。入内台中。见壁面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4H 页
 有苏学士笔额曰紫烟洞天。距今岁过百而遗芬如昨。摩挲久之。彷徨口吟。因登台上。有小屋三间。著巾老人见客换著笠。下阶迎。因坐行酒曰客与我同庚。故敢进情杯云。頫其庭矗矗石墩可十许仞。溪水触墩底隐不见。但闻山鸣谷应。若使坡老到此。必曰复睹石钟山也。傍有十数竿脩篁。挺绿于林端。庭畔数本花丛。欲发未发。含红吐香。两岸嘉木。挟墩成阴。无一点透阳。不风而凉生。樵采之往来于方丈者。必由台中。行歌以和。水声不鼓而自应。无非奇绝者。谓小屋主人曰自古溪山胜致。必有主张者传焉。钴潭得宗元而阐。兰亭遇逸少而名。今此无限名胜。寂寂在穷山荒谷中。何不妆点烟霞。今唱花竹。使一世知有春萝台。则后之韩士文。岂非柳宗元王逸少耶。主人曰苏学士先焉。余笑曰老人生长于此。栖息于此。即几案上物也。何必让与湖西古人苏学士乎。曰恨无文章如学士故耳。曰学士文章。吾未知其何如。而四字题壁。只一过去事也。学士平生遍历山川。或发口气。或留手迹。以此便谓之主。则学士当时。八域名胜。尽为学士有耶。老矣主人也。且无文章。宜乎让美于人也。遂别东转过新村。村则金进士养直旧居也。进士好饮酒善词赋。本湖南人而寓居于此。至老登庠云。至市街店午饭。望栗峙。老人欲前且却。吃吃作恶
有苏学士笔额曰紫烟洞天。距今岁过百而遗芬如昨。摩挲久之。彷徨口吟。因登台上。有小屋三间。著巾老人见客换著笠。下阶迎。因坐行酒曰客与我同庚。故敢进情杯云。頫其庭矗矗石墩可十许仞。溪水触墩底隐不见。但闻山鸣谷应。若使坡老到此。必曰复睹石钟山也。傍有十数竿脩篁。挺绿于林端。庭畔数本花丛。欲发未发。含红吐香。两岸嘉木。挟墩成阴。无一点透阳。不风而凉生。樵采之往来于方丈者。必由台中。行歌以和。水声不鼓而自应。无非奇绝者。谓小屋主人曰自古溪山胜致。必有主张者传焉。钴潭得宗元而阐。兰亭遇逸少而名。今此无限名胜。寂寂在穷山荒谷中。何不妆点烟霞。今唱花竹。使一世知有春萝台。则后之韩士文。岂非柳宗元王逸少耶。主人曰苏学士先焉。余笑曰老人生长于此。栖息于此。即几案上物也。何必让与湖西古人苏学士乎。曰恨无文章如学士故耳。曰学士文章。吾未知其何如。而四字题壁。只一过去事也。学士平生遍历山川。或发口气。或留手迹。以此便谓之主。则学士当时。八域名胜。尽为学士有耶。老矣主人也。且无文章。宜乎让美于人也。遂别东转过新村。村则金进士养直旧居也。进士好饮酒善词赋。本湖南人而寓居于此。至老登庠云。至市街店午饭。望栗峙。老人欲前且却。吃吃作恶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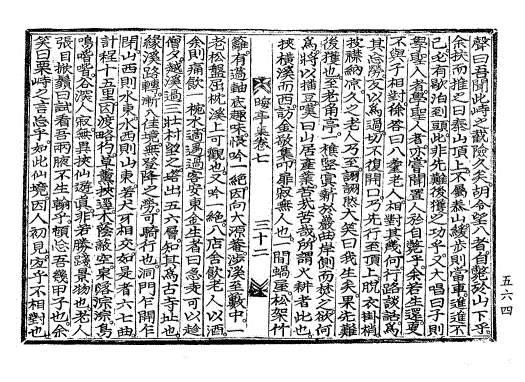 声曰吾闻此峙之截险久矣。胡令望八者。自毙于山下乎。余扶而推之曰泰山顶上。不属泰山。缓步则当车。进进不已。必有歇泊到头。此非先难后获之功乎。又大唱曰子则学圣人者。学圣人者。亦尝闻置人于自毙乎。余若生还。更不与子相对。徐答曰八耋老人。相对其几何。行路谈话。为其忘劳。反以为过。切不复开口。乃先行至顶上。脱衣挂梢。披襟纳凉。久之老人乃至。诩诩然大笑曰我生矣。果先难后获也。至老角亭。一樵竖寘薪于岩曲岸侧而焚之。欲何为。将以播豆。叹曰山居产业。苦哉苦哉。所谓火耕者此也。挟横溪而西。访金敬集。叩扉寂无人也。一间蜗屋。松架竹篱。有薖轴底趣味。怅吟一绝。因向大源庵。涉溪至薮中。一老松盘屈枕溪上可观也。又吟一绝。入店舍饮老人以酒。余则痛饮一碗水。适遇过客安东金生者曰急走可以趁僧夕。越溪过三壮村望之。塔出五六层。知其为古寺址也。缘溪路转。渐入佳境。无登降之劳。可骑行也。洞门乍开乍闭。山西则水东。水西则山东。若犬牙相交。如是者六七曲。计程十五里。因渡略彴。草薰挟径。木荫蔽空。泉落淙淙。鸟鸣喈喈。谷深人寂。无异挟仙游真。非若胜践景物也。老人张目掀须曰试看吾两腋不生翰乎。顿忘吾几甲子也。余笑曰栗峙之言忘乎。如此仙境。因人初见。宜乎不相对也。
声曰吾闻此峙之截险久矣。胡令望八者。自毙于山下乎。余扶而推之曰泰山顶上。不属泰山。缓步则当车。进进不已。必有歇泊到头。此非先难后获之功乎。又大唱曰子则学圣人者。学圣人者。亦尝闻置人于自毙乎。余若生还。更不与子相对。徐答曰八耋老人。相对其几何。行路谈话。为其忘劳。反以为过。切不复开口。乃先行至顶上。脱衣挂梢。披襟纳凉。久之老人乃至。诩诩然大笑曰我生矣。果先难后获也。至老角亭。一樵竖寘薪于岩曲岸侧而焚之。欲何为。将以播豆。叹曰山居产业。苦哉苦哉。所谓火耕者此也。挟横溪而西。访金敬集。叩扉寂无人也。一间蜗屋。松架竹篱。有薖轴底趣味。怅吟一绝。因向大源庵。涉溪至薮中。一老松盘屈枕溪上可观也。又吟一绝。入店舍饮老人以酒。余则痛饮一碗水。适遇过客安东金生者曰急走可以趁僧夕。越溪过三壮村望之。塔出五六层。知其为古寺址也。缘溪路转。渐入佳境。无登降之劳。可骑行也。洞门乍开乍闭。山西则水东。水西则山东。若犬牙相交。如是者六七曲。计程十五里。因渡略彴。草薰挟径。木荫蔽空。泉落淙淙。鸟鸣喈喈。谷深人寂。无异挟仙游真。非若胜践景物也。老人张目掀须曰试看吾两腋不生翰乎。顿忘吾几甲子也。余笑曰栗峙之言忘乎。如此仙境。因人初见。宜乎不相对也。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5H 页
 曰吾妄发矣。因抵寺门。竹风曳烟。磬声隐隐。登前楼。一衲即趍礼客曰远来良苦。夕供方张。引入房内。菜蔬可餐。疲卧稳寝。晨钟鏦鏦然搅耳。缁徒五六十。奔走汲供。余负手徊徨于厅上。见春帖诗云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辞甚萧爽。然非春帖之意也。至后苑。白头耆衲。舍锡合掌讫。引余入出一卷册。乃阙里祠记实也。祠在今华城府梧山之北。孔氏居此者甚蕃。 正庙末因多士请。自内阁摹圣像。妥于子姓所居而因名焉。录用其后故丹邱宰孔允东是已。擎玩一通曰此胡至此。老衲姓孔故贸来。而亦颇识文字者也。余曰子虽圣人之后。出家则异途也。祖如来而宗石虎。所尚者楞严圆觉足矣。岂以此置诸偈呗之案上乎。子可谓圣祖之罪人。阎浮之乱类也。老衲仆仆焉。余叹曰昔昌黎氏送文畅而惜其墨名儒行。今子亦近之耳。时石南居韩老人在傍。衣冠甚古。顾而语余曰此处奇绝。时又寂寥。可共一日之话乎。曰吾意然。相与登塔殿。韩老曰此庵据方丈东麓。山抱水涵。所谓壶中天地也。僧居以来。游散缰属。疲于供顿。然僧无离散。庵亦不贫。沙门福地。甲于此山。且塔殿基则青乌家以为金龟左掌。道场洁净。故藏舍利焉。塔盖九层也。第四前面坐寸许金佛。第六亦然。僧之言曰表其藏处也。环铺细石。石上设一蒲席。
曰吾妄发矣。因抵寺门。竹风曳烟。磬声隐隐。登前楼。一衲即趍礼客曰远来良苦。夕供方张。引入房内。菜蔬可餐。疲卧稳寝。晨钟鏦鏦然搅耳。缁徒五六十。奔走汲供。余负手徊徨于厅上。见春帖诗云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辞甚萧爽。然非春帖之意也。至后苑。白头耆衲。舍锡合掌讫。引余入出一卷册。乃阙里祠记实也。祠在今华城府梧山之北。孔氏居此者甚蕃。 正庙末因多士请。自内阁摹圣像。妥于子姓所居而因名焉。录用其后故丹邱宰孔允东是已。擎玩一通曰此胡至此。老衲姓孔故贸来。而亦颇识文字者也。余曰子虽圣人之后。出家则异途也。祖如来而宗石虎。所尚者楞严圆觉足矣。岂以此置诸偈呗之案上乎。子可谓圣祖之罪人。阎浮之乱类也。老衲仆仆焉。余叹曰昔昌黎氏送文畅而惜其墨名儒行。今子亦近之耳。时石南居韩老人在傍。衣冠甚古。顾而语余曰此处奇绝。时又寂寥。可共一日之话乎。曰吾意然。相与登塔殿。韩老曰此庵据方丈东麓。山抱水涵。所谓壶中天地也。僧居以来。游散缰属。疲于供顿。然僧无离散。庵亦不贫。沙门福地。甲于此山。且塔殿基则青乌家以为金龟左掌。道场洁净。故藏舍利焉。塔盖九层也。第四前面坐寸许金佛。第六亦然。僧之言曰表其藏处也。环铺细石。石上设一蒲席。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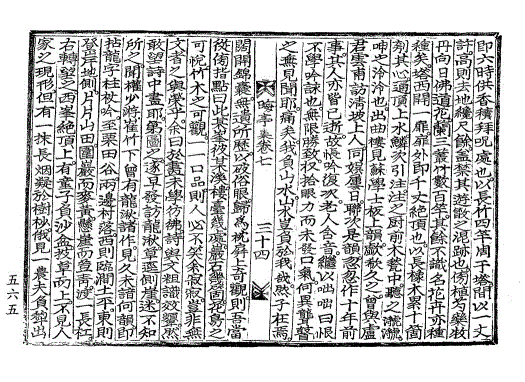 即六时供香积拜咒处也。以长竹四竿周于塔。间以一丈许。高则去地才尺馀。盖禁其游散之混迹也。傍植芍药牧丹向日佛道花。兰三丛竹数百竿。其馀不识名花卉亦种种矣。塔西开一扉。扉外即千丈绝顶也。以长橡木累十个刳其心。通顶上水。鳞次引注。注之厨前木甃中。听之㶁㶁。呻之泠泠也。出曲楼见苏学士板上韵。歔欷久之。曾与卢君云甫访清坡上人。同娱屡日。联次是韵。忽忽作十年前事。其人亦皆已逝。故怅吟复次。老人含音。继以咄咄曰恨不学吟咏也。无限胜致。收拾眼力而未发口气。何异聋瞽之无见闻耶。痛矣。我负山水。山水岂负于我哉。然子在焉。阔开锦囊。无遗所历。以破俗眼。归为枕屏上奇观。则吾当从傍指点曰此某峰彼某溪。楼台几处。岩石几个。花鸟之可悦。竹木之可观。一一口品。则人必不笑余寂寂。岂非无文者之与荣乎。余曰于画未学彷佛。诗与文粗识效颦。然敢望诗中画耶。第图之。遂早发访龙湫。草径侧崖。迷不知所之。闻权少游,崔竹下曾有龙湫诸作。见久未谙何韵。即拈龙字柱杖吟。至栗田谷。两边村落。西则临涧土平。东则登岸地侧。片片山田。围岩而麦黄。悬崖而豆青。渡一长杠。右转望之。西峰绝顶上。有童子负沙盆。披草而上。不见人家之现形。但有一抹长烟凝于树杪。俄见一农夫负犁出
即六时供香积拜咒处也。以长竹四竿周于塔。间以一丈许。高则去地才尺馀。盖禁其游散之混迹也。傍植芍药牧丹向日佛道花。兰三丛竹数百竿。其馀不识名花卉亦种种矣。塔西开一扉。扉外即千丈绝顶也。以长橡木累十个刳其心。通顶上水。鳞次引注。注之厨前木甃中。听之㶁㶁。呻之泠泠也。出曲楼见苏学士板上韵。歔欷久之。曾与卢君云甫访清坡上人。同娱屡日。联次是韵。忽忽作十年前事。其人亦皆已逝。故怅吟复次。老人含音。继以咄咄曰恨不学吟咏也。无限胜致。收拾眼力而未发口气。何异聋瞽之无见闻耶。痛矣。我负山水。山水岂负于我哉。然子在焉。阔开锦囊。无遗所历。以破俗眼。归为枕屏上奇观。则吾当从傍指点曰此某峰彼某溪。楼台几处。岩石几个。花鸟之可悦。竹木之可观。一一口品。则人必不笑余寂寂。岂非无文者之与荣乎。余曰于画未学彷佛。诗与文粗识效颦。然敢望诗中画耶。第图之。遂早发访龙湫。草径侧崖。迷不知所之。闻权少游,崔竹下曾有龙湫诸作。见久未谙何韵。即拈龙字柱杖吟。至栗田谷。两边村落。西则临涧土平。东则登岸地侧。片片山田。围岩而麦黄。悬崖而豆青。渡一长杠。右转望之。西峰绝顶上。有童子负沙盆。披草而上。不见人家之现形。但有一抹长烟凝于树杪。俄见一农夫负犁出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6H 页
 林间。黑牛在前。随后者黄犊也。回绝顶向山田望之。若画中景也。时朝阳乍透。草露未晞。二人遂脱氅衣。带以荷之。行三里。嘉木荫路。巨岩环溪。水之游者潭之。走者瀑之。甚奇绝处也。遂坐移时。浪吟一绝。已而一人踝跣而至。问之姓金也。自东都移寓于榆杜里已八年云。余曰不善变也。出自乔木。迁于幽谷耶。金生曰莫非王土。何往非民。而所取者渔樵无禁。耕种无税耳。曰既为王民则何以取无税。子将以榆杜里为武陵源耶。东都未尝无山而胡此远为。曰方欲出山而移巢之鸟。投处深林。故姑留未返。然每月明夜寂。有鸟唤归蜀道。声声则悽然。发不平怀想。或微雨过林。白云宿檐。飞泉泻淙。娇莺学音。樵歌采谣。相应于穷山深薮中则自不觉山居兴味之凝然挑出。吾未知武陵之如何。而隔绝人烟。想必如是。所恨者无桃花也。余怃然曰子固隐矣。长往不返也。因与行百馀武。路岐当前。左而涉溪。溪之边一草幕搆之。壁未乾也。老婆衣装甚鲜。酾酒方壶。老人痛饮三碗曰孰谓山中无别味。且有山中贵物也。别味虽饮而贵物难亲。可恨可恨。老婆知其戏言。答曰人皆可亲。岂为贵物乎。别味足矣。相与呵呵。余劝金生饮二杯。甚喜之。遂登顶行一里许。谷中作局。有上下村。上六家下十三家矣。生入檐下石广。俄而出。右手举炉。左手掬
林间。黑牛在前。随后者黄犊也。回绝顶向山田望之。若画中景也。时朝阳乍透。草露未晞。二人遂脱氅衣。带以荷之。行三里。嘉木荫路。巨岩环溪。水之游者潭之。走者瀑之。甚奇绝处也。遂坐移时。浪吟一绝。已而一人踝跣而至。问之姓金也。自东都移寓于榆杜里已八年云。余曰不善变也。出自乔木。迁于幽谷耶。金生曰莫非王土。何往非民。而所取者渔樵无禁。耕种无税耳。曰既为王民则何以取无税。子将以榆杜里为武陵源耶。东都未尝无山而胡此远为。曰方欲出山而移巢之鸟。投处深林。故姑留未返。然每月明夜寂。有鸟唤归蜀道。声声则悽然。发不平怀想。或微雨过林。白云宿檐。飞泉泻淙。娇莺学音。樵歌采谣。相应于穷山深薮中则自不觉山居兴味之凝然挑出。吾未知武陵之如何。而隔绝人烟。想必如是。所恨者无桃花也。余怃然曰子固隐矣。长往不返也。因与行百馀武。路岐当前。左而涉溪。溪之边一草幕搆之。壁未乾也。老婆衣装甚鲜。酾酒方壶。老人痛饮三碗曰孰谓山中无别味。且有山中贵物也。别味虽饮而贵物难亲。可恨可恨。老婆知其戏言。答曰人皆可亲。岂为贵物乎。别味足矣。相与呵呵。余劝金生饮二杯。甚喜之。遂登顶行一里许。谷中作局。有上下村。上六家下十三家矣。生入檐下石广。俄而出。右手举炉。左手掬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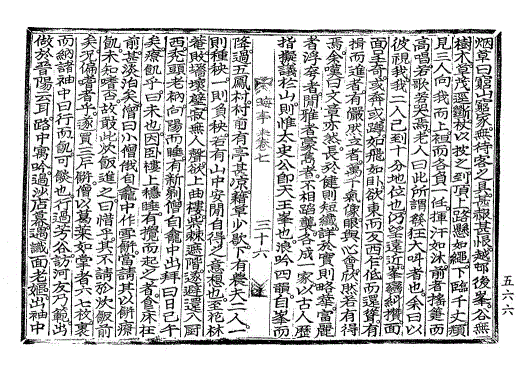 烟草曰穷山穷家。无待客之具。甚赧甚恨。越村后峰。谷无树木。草茂径断。杖以披之。到顶上。路悬如绳。下临千丈。頫见三人向我而上。袒而各负一任。挥汗如沐。前者摇箑而高唱。若歌若哭焉。老人曰此所谓发狂大叫者也。余曰以彼视我。我二人已到十分地位也。仍望远近。峰峦纠攒。面面呈奇。或奔或蹲。如飞如卧。欲东而反西。乍低而还耸。有揖而进者。有俨然立者。万千气像。眼与心会。欣然若有得焉。余叹曰文章亦然。长于健则短纤。详于实则略华。富丽者浮夸者。閒雅者豪隽者。不相蹈袭。各成一家。以古人历指拟议于山。则惟太史公即天王峰也。浪吟四韵。自峰而降。过五凤村。村前有亭甚凉。藉草少歇。下有农夫二人。一则种秧。一则负秧。若有山中安閒自得之意想也。至花林庵。败墙坏壁。寂无人声。欲上曲楼。柴棘遮阶。遂避还入厨西。秃头老衲。向阳而睡。有新剃僧自龛中出拜曰日已午矣。疗饥乎。曰未也。因卧楼上稳睡。有搅而起之者。食床在前。甚淡泊矣。僧曰小僧俄自龛中作雪饼。当请其以饼疗饥。未知嗜否。故敢此炊饭进之。曰惜乎。其不请于炊饭前矣。况偏嗜者乎。遂买三片饼。僧以葛叶如掌者六七枚。裹而纳诸袖中曰行而饥。可餤也。行过芳谷。访河友乃范。出做于晋阳云耳。路中寓吟。过沙店幕。遇识面老妪。出袖中
烟草曰穷山穷家。无待客之具。甚赧甚恨。越村后峰。谷无树木。草茂径断。杖以披之。到顶上。路悬如绳。下临千丈。頫见三人向我而上。袒而各负一任。挥汗如沐。前者摇箑而高唱。若歌若哭焉。老人曰此所谓发狂大叫者也。余曰以彼视我。我二人已到十分地位也。仍望远近。峰峦纠攒。面面呈奇。或奔或蹲。如飞如卧。欲东而反西。乍低而还耸。有揖而进者。有俨然立者。万千气像。眼与心会。欣然若有得焉。余叹曰文章亦然。长于健则短纤。详于实则略华。富丽者浮夸者。閒雅者豪隽者。不相蹈袭。各成一家。以古人历指拟议于山。则惟太史公即天王峰也。浪吟四韵。自峰而降。过五凤村。村前有亭甚凉。藉草少歇。下有农夫二人。一则种秧。一则负秧。若有山中安閒自得之意想也。至花林庵。败墙坏壁。寂无人声。欲上曲楼。柴棘遮阶。遂避还入厨西。秃头老衲。向阳而睡。有新剃僧自龛中出拜曰日已午矣。疗饥乎。曰未也。因卧楼上稳睡。有搅而起之者。食床在前。甚淡泊矣。僧曰小僧俄自龛中作雪饼。当请其以饼疗饥。未知嗜否。故敢此炊饭进之。曰惜乎。其不请于炊饭前矣。况偏嗜者乎。遂买三片饼。僧以葛叶如掌者六七枚。裹而纳诸袖中曰行而饥。可餤也。行过芳谷。访河友乃范。出做于晋阳云耳。路中寓吟。过沙店幕。遇识面老妪。出袖中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7H 页
 物与之。至自礼村拜于墓所。访梁丈到帆川。朴友极老自湖南新寓者也。问其家。即其扉外也。一婢阿鲜衫青裙。引入于庭中曰客从何处。曰大浦来也。主人自内而出曰今日之行。为我委访耶历访耶。余曰子之问。欲试吾情之疏密。待之有厚薄耶。吾性简傲。于交人淡泊无昵密。以汎爱观之。海内皆兄弟也。安有疏则历访。密则委访乎。极老曰非谓此也。子素不喜一脚出门。忽此辱临。故惊喜猝问耳。余笑曰苟知为然。岂非委访乎。相对握握遂强。余脱衣冠。授以枕。忽有二青童以丛竹苞献主人曰自牛头来。视之江鱼也。余笑曰吾听厥童之言。始信肉矣。胡乃鱼耶。极老曰牛头村名也。所亲某为我送此。此时此物。犹胜于安邑之猪肝。不逊于江州之菊酒也。急呼青裙婢脍以肴之。劝余以酒。酒则辞以未能。极老曰虽知素不好饮。而美人所劝。安可恝然乎。强饮数匙。乘醉终宵噱谈。朝后携手出松林。循江而下。回至书堂。丹城权生亦在焉。复呼酒作别。出江上指路。有一墩杂土石临汀。若孤帆之出海上。村之名以是故也。遵汀寻路。路中口吟。行至舟岩。十数衣冠。列坐亭下。乃鹅湖郑上舍,愚溪河老丈诸人也。方设川猎。强余同娱。固辞将发。老人唱于座曰今行与少年作伴。所辱者夥矣。逢此侪辈。正吾得意秋也。子独行矣。子独行矣。叩山
物与之。至自礼村拜于墓所。访梁丈到帆川。朴友极老自湖南新寓者也。问其家。即其扉外也。一婢阿鲜衫青裙。引入于庭中曰客从何处。曰大浦来也。主人自内而出曰今日之行。为我委访耶历访耶。余曰子之问。欲试吾情之疏密。待之有厚薄耶。吾性简傲。于交人淡泊无昵密。以汎爱观之。海内皆兄弟也。安有疏则历访。密则委访乎。极老曰非谓此也。子素不喜一脚出门。忽此辱临。故惊喜猝问耳。余笑曰苟知为然。岂非委访乎。相对握握遂强。余脱衣冠。授以枕。忽有二青童以丛竹苞献主人曰自牛头来。视之江鱼也。余笑曰吾听厥童之言。始信肉矣。胡乃鱼耶。极老曰牛头村名也。所亲某为我送此。此时此物。犹胜于安邑之猪肝。不逊于江州之菊酒也。急呼青裙婢脍以肴之。劝余以酒。酒则辞以未能。极老曰虽知素不好饮。而美人所劝。安可恝然乎。强饮数匙。乘醉终宵噱谈。朝后携手出松林。循江而下。回至书堂。丹城权生亦在焉。复呼酒作别。出江上指路。有一墩杂土石临汀。若孤帆之出海上。村之名以是故也。遵汀寻路。路中口吟。行至舟岩。十数衣冠。列坐亭下。乃鹅湖郑上舍,愚溪河老丈诸人也。方设川猎。强余同娱。固辞将发。老人唱于座曰今行与少年作伴。所辱者夥矣。逢此侪辈。正吾得意秋也。子独行矣。子独行矣。叩山晦亭集卷之七 第 5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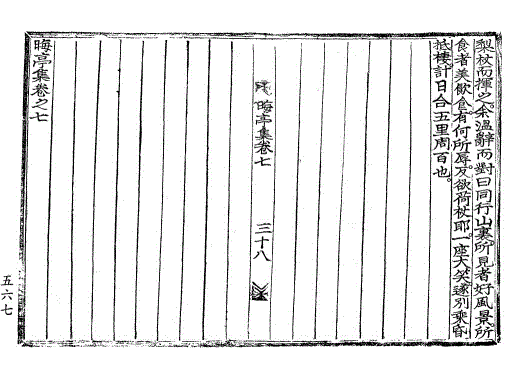 梨杖而挥之。余温辞而对曰同行山里。所见者好风景。所食者美饮食。有何所辱。反欲荷杖耶。一座大笑。遂别乘昏抵栖。计日合五里周百也。
梨杖而挥之。余温辞而对曰同行山里。所见者好风景。所食者美饮食。有何所辱。反欲荷杖耶。一座大笑。遂别乘昏抵栖。计日合五里周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