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x 页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杂著
杂著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07H 页
 大学劄疑 并小序(저본의 원목차에 근거하여 并小序를 보충하였다.)○甲申
大学劄疑 并小序(저본의 원목차에 근거하여 并小序를 보충하였다.)○甲申往在己卯冬。读大学。有疑辄记。读毕便忘。不复捡阅。间重读是书。乃取前所为说而观焉。类皆摸捞皮膜浅陋可厌也。吁余自己卯而后。诱夺益深。冗忧益攻。于此一边盖专倚阁矣。然一番寻绎。犹觉见解稍进。讲读古书。其可废也哉。乃就前说中。逐旋删补。亦非敢以为得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前。则斯亦异日自省之一助云。
经明德。 明德者。只是本心之明。非有他也。(言心则包性情在其中。)但大学立言。要人见得这个光明之体。得之于天。而众理咸备。万用俱足。有不可以自我失之之意。则心字虽无所不包。而未有以辄见得这般意思也。且其得名。自是理气滚合底。则其纯粹浑全。又岂若德字乎。盖德之为言得也。便见他天所授人所得而纯粹具足。不容暂失之意。此其所以不曰明心。而特言明德者欤。或疑此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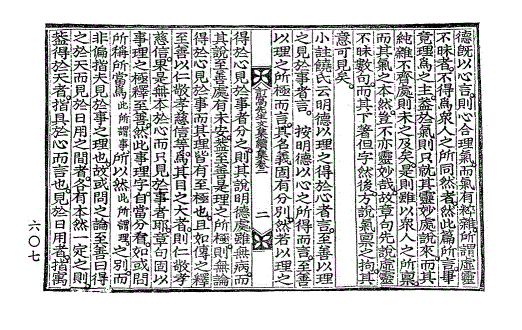 德既以心言。则心合理气。而气有粹杂。所谓虚灵不昧者。不得为众人之所同然者。然此篇所言。毕竟理为之主。盖于气则只就其灵妙处说来。而其纯杂不齐处则未之及矣。是则虽以众人之所禀。而其气之本然。岂不亦灵妙哉。故章句先说虚灵不昧数句。而其下著但字然后。方说气禀之拘。其意可见矣。
德既以心言。则心合理气。而气有粹杂。所谓虚灵不昧者。不得为众人之所同然者。然此篇所言。毕竟理为之主。盖于气则只就其灵妙处说来。而其纯杂不齐处则未之及矣。是则虽以众人之所禀。而其气之本然。岂不亦灵妙哉。故章句先说虚灵不昧数句。而其下著但字然后。方说气禀之拘。其意可见矣。小注饶氏云明德以理之得于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见于事者言。 按明德以心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极而言。其名义固有分别。然若以理之得于心见于事者分之。则其说明德处虽无病。而其说至善处有未安。盖至善是理之所极。则无论得于心见于事而其理皆有至极也。且如传之释至善以仁敬孝慈信等。为其目之大者。则仁敬孝慈信。果是无本于心而只见于事者耶。章句固以事理之极释至善。然此事理字。自当分看。如或问所称所当为(此所谓事。)所以然(此所谓理。)之别。而非偏指夫见于事之理也。故或问之论至善曰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各有本然一定之则。盖得于天者。指具于心而言也。见于日用者。指寓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08H 页
 于事而言也。饶氏之说。盖亦未察于此欤。
于事而言也。饶氏之说。盖亦未察于此欤。吴氏云事理是理之万殊处。天理是理之一本处。 事理二字。前段略及。而其变事理言天理者。只是对人欲而言。非有别意也。若如吴氏万殊一本之云。则其言事理当然之极者。是正释至善也。其言尽夫天理之极者。既正释而统论之也。何必于正释之时。偏指其万殊处。而统论之时。乃及其一本处也。如此则上下所说。各有所偏而有欠于文理矣。
逆推工夫。顺推功效。 君子之学。规模甚大。而进为有序。故立志则必先远大。而收效则不容躐易。所以于工夫则自平天下而逆推之。以示其规模之大。而有所向望而立志也。于功效则自物格而顺推之。以示其进为之序。而有所持循而收效也。
物理之极处无不到。 章句以至训格。而以极处无不到。训物格。盖至字与到字。以工夫言则微有自此到彼之意。而以功效言则只为极尽之意。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云者。盖我能穷至于物。则物之理自到尽。如人之行路。行尽而路亦尽也。或者作来到字看。则事物之理。本自无情。而极处云者。又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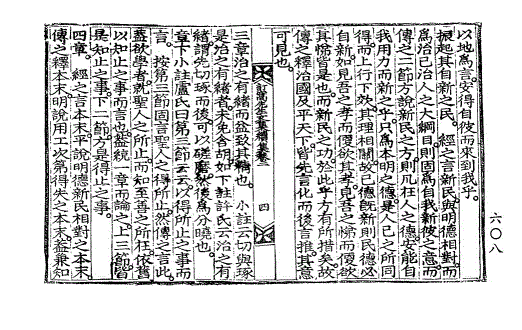 以地为言。安得自彼而来到我乎。
以地为言。安得自彼而来到我乎。振起其自新之民。 经之言新民。与明德相对。而为治己治人之大纲目。则固为自我新彼之意。而传之二节方说新民之方。则凡在人之德。安能自我用力而新之乎。只为本明之德。是人己之所同得。而上行下效。其理相关。故己德既新则民德必自新。如见吾之孝而便欲其孝。见吾之悌而便欲其悌皆是也。而新民之功。于此乎方有所措矣。故传之释治国及平天下。皆先言化而后言推。其意可见也。
三章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 小注云切与琢是治之有绪者。未免含胡。如下注许氏云治之有绪。谓先切琢而后。可以磋磨。然后为分晓也。
章下小注卢氏曰第三节云云。以得所止之事而言。 按第三节固言圣人之得所止。然传之言此。盖欲学者。就圣人之所止。而知至善之所在。依旧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盖统一章而论之。上三节。皆是知止之事。下二节。方是得止之事。
四章。 经之言本末。平说明德新民相对之本末。传之释本末。明说用工次第得失之本末。盖兼知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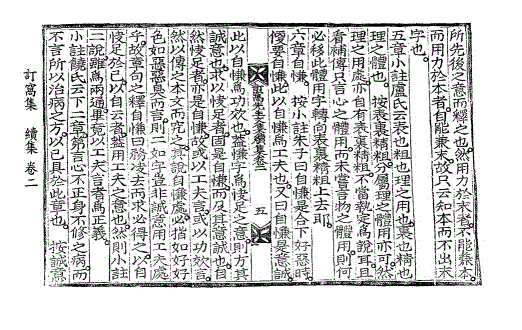 所先后之意而释之也。然用力于末者。不能兼本。而用力于本者。自能兼末。故只云知本而不出末字也。
所先后之意而释之也。然用力于末者。不能兼本。而用力于本者。自能兼末。故只云知本而不出末字也。五章小注卢氏云表也粗也理之用也。里也精也理之体也。 按表里精粗。分属理之体用亦可。然理之用处。亦自有表里精粗。不当执定为说耳。且看补传只言心之体用。而未尝言物之体用。则何必移此体用字转向表里精粗上去耶。
六章自慊。 按小注朱子曰自慊是合下好恶时。便要自慊。此以自慊为工夫也。又曰自慊是意诚。此以自慊为功效也。盖慊字为快足之意。则方其诚意也。求以快足者。固是自慊。而及其意诚也。自然快足者。亦是自慊。故或以工夫言。或以功效言。然以传之本文而究之。其说自慊处。必指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而言。则二如字岂非诚意用工夫处乎。故章句之释自慊曰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以自云者。盖用工夫之意也。然则小注二说。虽为两通。毕竟以工夫言者为正义。
小注饶氏云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于此章也。 按诚意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09L 页
 为善恶关。于此透不过则基本不立而不无躐进之理。于此透得过则工夫甚省而渐有驯致之功。故传之释诚意。特详于正心修身。而其释正心修身则又较略于诚意。盖随其用力之难易而立言有别也。然就正心修身二章而论之。其所以言不正不修之病者。乃所以示正之修之之方。盖知如此为病。则知不如此为无病耳。且其所说喜怒忧惧之用。爱恶敬惰之则。皆明指其用工地头而言。则治病之方。岂可外此而他求哉。盖大学八目。节节有工夫在。意虽已诚而不可无正心工夫。心虽已正而不可无修身工夫。此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矣。而饶氏于此既失之。其论心广体胖一段。又曰心不正。何以能广。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广体胖。即心正身修之验。此亦不然。盖心广体胖。是意诚后自慊气象。而正与广修与胖。所言自别。则是其喜怒忧惧之用。不可以既广而不察焉。爱恶敬惰之则。不可以既胖而不捡焉。此岂可赚著于心体二字。而遽以为正修之效也哉。大抵饶氏之说。于诚意之为要妙处则得矣。而于下面许多工夫。便一齐掉了。是则圣门之述大学。只当言致
为善恶关。于此透不过则基本不立而不无躐进之理。于此透得过则工夫甚省而渐有驯致之功。故传之释诚意。特详于正心修身。而其释正心修身则又较略于诚意。盖随其用力之难易而立言有别也。然就正心修身二章而论之。其所以言不正不修之病者。乃所以示正之修之之方。盖知如此为病。则知不如此为无病耳。且其所说喜怒忧惧之用。爱恶敬惰之则。皆明指其用工地头而言。则治病之方。岂可外此而他求哉。盖大学八目。节节有工夫在。意虽已诚而不可无正心工夫。心虽已正而不可无修身工夫。此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矣。而饶氏于此既失之。其论心广体胖一段。又曰心不正。何以能广。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广体胖。即心正身修之验。此亦不然。盖心广体胖。是意诚后自慊气象。而正与广修与胖。所言自别。则是其喜怒忧惧之用。不可以既广而不察焉。爱恶敬惰之则。不可以既胖而不捡焉。此岂可赚著于心体二字。而遽以为正修之效也哉。大抵饶氏之说。于诚意之为要妙处则得矣。而于下面许多工夫。便一齐掉了。是则圣门之述大学。只当言致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0H 页
 知诚意以下。接齐治平之事足矣。何必更以没紧底剩语。叠架于其间乎。
知诚意以下。接齐治平之事足矣。何必更以没紧底剩语。叠架于其间乎。七章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 心之不正其可见者。在用而不在体。故章句之言不正。专指用之所行。然所谓一有之及欲动情胜者。皆是前事已过。后事未来时里面底事。则下梢不正之病。却根于体矣。然则正心工夫。正当兼体用做工夫。以体则虚而存之。以用则审而察之。然后方免于不正也。
八章诚正修三条。 诚正修三条。皆就心上用工。然其间各有分别。盖心对意言则意是发处而心是全体。身对心言则心是里面而身是外面。故意诚则心之发处。已能好善恶恶而真实无杂。然意诚而不能存其心。则其全体寂感之妙。或不能无失于逐物系著之际矣。此其所失。非如自欺之弊。全为不善。而亦善中之病也。心正则身之里面已能体存用适而虚静无累。然心正而不能检其身。则其外面接应之则。不能无偏于因人爱恶之际。此其为病。非若有所之累。全为不正。而亦正中之失也。是则诚正修三条。安得不各致其功耶。愚尝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0L 页
 取喻于水。诚意者淘其泥滓而无所污杂也。正心者。止其波浪而无所蹴痕也。修身者理其堤岸而无所荫蔽也。
取喻于水。诚意者淘其泥滓而无所污杂也。正心者。止其波浪而无所蹴痕也。修身者理其堤岸而无所荫蔽也。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 按经文既详说八事。而其末段复拈出修齐两事以结之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盖以身与家是人己之际接。家与国是亲疏之际接。恐人之视之。较为间阔。故重指其相关之机。而尤致其丁宁之意焉。是以传者。于修齐章末则反语而结之。以应本乱末治者否之语。于齐治章首则加必先字。以应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意。其立文命意。接续贯通。不容放过。有如是夫。
九章章句立教之本。在识其端云云。而卢氏云本者明德是也。端者明德之发见。为孝悌慈是已。 按立教之本。指孝悌慈而言。其端则心诚求之者是已。卢氏乃以本为明德。而以端方为孝悌慈。夫本之一字。推而言之则谓之明德亦可。然自本文观之。直是看得蓦越。至所谓端则分明就孝悌慈中指其萌动之自然者而言。何必向端字下面。方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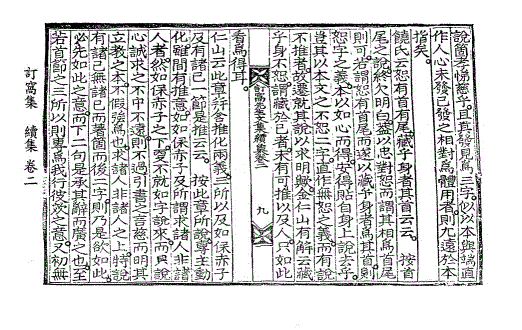 说个孝悌慈乎。且其发见为三字。似以本与端直作人心未发已发之相对为体用者。则尤远于本指矣。
说个孝悌慈乎。且其发见为三字。似以本与端直作人心未发已发之相对为体用者。则尤远于本指矣。饶氏云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云云。 按首尾之说。终欠明白。盖以忠对恕而谓其相为首尾则可。若谓恕有首尾而遂以藏乎身者为其首。则恕字之义。本以如心而得。安得贴自身上说去乎。岂其以本文之不恕二字。直作无恕之义。而有说不推者。故迁就其说以求明欤。金仁山有解云藏乎身不恕。谓藏于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只如此看为得耳。
仁山云此章并含推化两义。三所以及如保赤子及有诸己一节是推云云。 按此章所说。专主动化。虽间有推意。如如保赤子及所谓求诸人非诸人者。然如保赤子之下。更不就如字说来。而只说心诚求之不中不远。则不过引书之言慈而明其立教之本。不假强为也。求诸人非诸人之上。特说有诸己无诸己而著个而后二字。则乃是欲如此。必先如此之意。而下二句是承其辞而广之也。至若首节之三所以则专为我行彼效之意。又初无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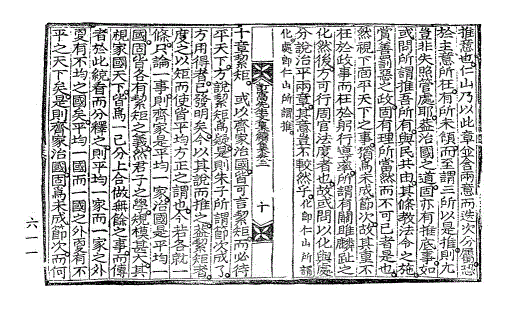 推意也。仁山乃以此章并含两意而迭次分属。恐于主意所在。有所未领。而至谓三所以是推。则尤岂非失照管处耶。盖治国之道。固亦有推底事。如或问所谓推吾所有。与民共由。其条教法令之施。赏善罚恶之政。固有理所当然而不可已者是也。然视下面平天下之事。犹为未成节次。故其重不在于政事而在于躬行导率。所谓有关雎麟趾之化然后。方可行周官法度者也。故或问以化与处分说治平两章。其意岂不较然乎。(化即仁山所谓化。处即仁山所谓推。)
推意也。仁山乃以此章并含两意而迭次分属。恐于主意所在。有所未领。而至谓三所以是推。则尤岂非失照管处耶。盖治国之道。固亦有推底事。如或问所谓推吾所有。与民共由。其条教法令之施。赏善罚恶之政。固有理所当然而不可已者是也。然视下面平天下之事。犹为未成节次。故其重不在于政事而在于躬行导率。所谓有关雎麟趾之化然后。方可行周官法度者也。故或问以化与处分说治平两章。其意岂不较然乎。(化即仁山所谓化。处即仁山所谓推。)十章絜矩。 或以齐家治国。皆可言絜矩。而必待平天下。方说絜矩为疑。是则朱子所谓节次成了。方用得者。已发明矣。今以其说而推之。盖絜矩者。度之以矩而使皆平均方正之谓也。今若各就一条。只论一事。则齐家是平均一家。治国是平均一国。固皆各有絜矩之义。然君子之学。规模甚大。其视家国天下。皆为一己分上合做无馀之事。而传者于此统看而分释之。则平均一家而一家之外更有不均之国矣。平均一国而一国之外更有不平之天下矣。是则齐家治国。固为未成节次。而何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2H 页
 足以尽絜矩之量也哉。必须统天下为一。而凡上下四旁。各极其无外然后。所谓平均方正者。方尽其限耳。此其所谓节次成了。方用得者欤。
足以尽絜矩之量也哉。必须统天下为一。而凡上下四旁。各极其无外然后。所谓平均方正者。方尽其限耳。此其所谓节次成了。方用得者欤。章句存此心而不失云云。而卢氏云存此心而不失则明德之体所以立。 按存此心而不失云者。是指峻命不易。而欲其存此警惧之心。非以本原上存养工夫而言也。卢氏乃谓存此心而不失则明德之体立。恐亦赚看而失其指矣。
或问敬为圣学之始终。小注卢云敬者定志虑摄精神存养本心之道。故为圣学之始终。 按存养本心之下。须带说开发聪明进德修业等意思然后。当得学之始终者。方周密无欠矣。
析之极其精。合之尽其大。小注卢氏云析之极其精则知吾心之用无不贯。合之尽其大则知吾心之体无不该。 按析之以下。看得甚易。析之极其精。是指明德新民分析说去。合之尽其大。是指明明德于天下衮合说来。若所谓吾心之体无不该。吾心之用无不贯。则皆属合之尽其大一句耳。卢氏却分体用二语。对属析合二句。其离了本指远矣。至引真西山小大一贯之说以證其言。则岂西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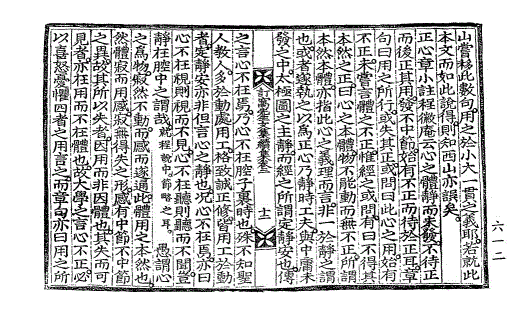 山尝移此数句。用之于小大一贯之义耶。若就此本文而如此说得。则知西山亦误矣。
山尝移此数句。用之于小大一贯之义耶。若就此本文而如此说得。则知西山亦误矣。正心章小注程徽庵云心之体静而未发。不待正而后正其用。发不中节。始有不正而待于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问曰此心之用。始有不正。未尝言体之不正。惟经之或问。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所谓本然本体。亦指此心之义理而言。非一于静之谓也。或者遂执之以为正心乃静时工夫。与中庸未发之中。太极图之主静。而经之所谓定静安也。传之言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里时也。殊不知圣人教人。多于动处用工。格致诚正修。皆用工于动者。定静安亦非但言心之静也。况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视则视而不见。心不在听则听而不闻。岂静在腔中之谓哉。(就程说中。节略之耳。) 愚谓心之为物。寂然不动。而感而遂通。此体用之本然也。然体寂而用感。寂无得失之形。感有中节不中节之异。故其所以失者。因用而非因体也。其失而可见者。亦在用而不在体也。故大学之言心不正。必以喜怒忧惧四者之用言之。而章句亦曰用之所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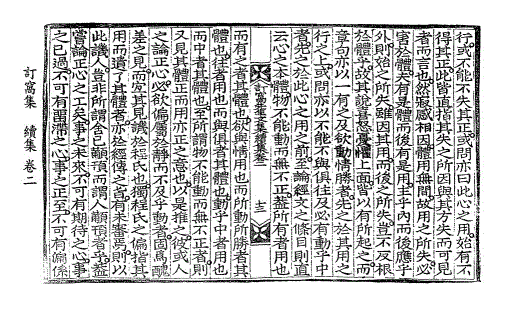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或问亦曰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此皆直指其失之所因与其方失而可见者而言也。然寂感相因。体用无间。故用之所失。必害于体。夫有是体而后有是用。主乎内而后应乎外。则始之所失。虽因其用。而后之所失。岂不反根于体乎。故其说喜怒忧惧上面。皆以有所起之。而章句亦以一有之及欲动情胜者。先之于其用之行之上。或问亦以不能不与俱往及必有动乎中者。先之于此心之用之前。至论经文之条目则直云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盖所有者用也而有之者其体也。欲与情用也而所动所胜者其体也。往者用也而与俱者其体也。动乎中者用也而中者其体也。至所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者。则又见其体正而用亦正之意也。以是推之。彼或人之论正心。必欲偏属于静而不及乎动者。固为丑差之见。而宜其见讥于程氏也。独程氏之偏指其用而遗了其体者。亦于经传之旨。有未审焉。则以此讥人。岂非所谓舍己颟顸而谓人颟顸者乎。盖尝论正心之工矣。事之未来。不可有期待之心。事之已过。不可有留滞之心。事之正至。不可有偏系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或问亦曰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此皆直指其失之所因与其方失而可见者而言也。然寂感相因。体用无间。故用之所失。必害于体。夫有是体而后有是用。主乎内而后应乎外。则始之所失。虽因其用。而后之所失。岂不反根于体乎。故其说喜怒忧惧上面。皆以有所起之。而章句亦以一有之及欲动情胜者。先之于其用之行之上。或问亦以不能不与俱往及必有动乎中者。先之于此心之用之前。至论经文之条目则直云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盖所有者用也而有之者其体也。欲与情用也而所动所胜者其体也。往者用也而与俱者其体也。动乎中者用也而中者其体也。至所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者。则又见其体正而用亦正之意也。以是推之。彼或人之论正心。必欲偏属于静而不及乎动者。固为丑差之见。而宜其见讥于程氏也。独程氏之偏指其用而遗了其体者。亦于经传之旨。有未审焉。则以此讥人。岂非所谓舍己颟顸而谓人颟顸者乎。盖尝论正心之工矣。事之未来。不可有期待之心。事之已过。不可有留滞之心。事之正至。不可有偏系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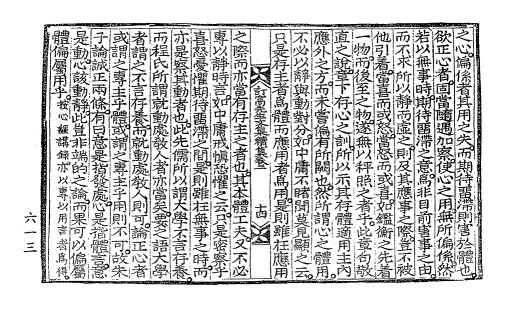 之心。偏系者其用之失。而期待留滞则害于体也。欲正心者。固当随遇加察。使心之用。无所偏系。然若以无事时。期待留滞之意。为非目前害事之由。而不求所以静而虚之。则及其应事之际。岂不被他引着。当喜而或怒。当怒而或喜。如鉴衡之先着一物。而后至之物。遂无以秤照之者乎。此章句敬直之说。章下存心之训。所以示其存体适用主内应外之方。而未尝偏有所阙也。然所谓心之体用。不必以静与动对分。如中庸不睹闻莫见显之云。只是存主者为体而应用者为用。是则虽在应用之际而亦当有存主之者也。其本体工夫。又不必专以静时言。如中庸戒慎恐惧之云。只是密察乎喜怒忧惧期待留滞之间。是则虽在无事之时。而亦是察其动者也。此先儒所以谓大学不言存养。而程氏所谓就动处教人者亦当矣。要之语大学者谓之不言存养。而就动处教人则可。论正心者或谓之专主乎体。或谓之专主乎用则不可。故朱子论诚正两条。有曰意是指发处。心是指体言。意是动。心该动静。此岂非端的之论。而果可以偏属体偏属用乎。(按心经讲录。亦以专以用言者为得。
之心。偏系者其用之失。而期待留滞则害于体也。欲正心者。固当随遇加察。使心之用。无所偏系。然若以无事时。期待留滞之意。为非目前害事之由。而不求所以静而虚之。则及其应事之际。岂不被他引着。当喜而或怒。当怒而或喜。如鉴衡之先着一物。而后至之物。遂无以秤照之者乎。此章句敬直之说。章下存心之训。所以示其存体适用主内应外之方。而未尝偏有所阙也。然所谓心之体用。不必以静与动对分。如中庸不睹闻莫见显之云。只是存主者为体而应用者为用。是则虽在应用之际而亦当有存主之者也。其本体工夫。又不必专以静时言。如中庸戒慎恐惧之云。只是密察乎喜怒忧惧期待留滞之间。是则虽在无事之时。而亦是察其动者也。此先儒所以谓大学不言存养。而程氏所谓就动处教人者亦当矣。要之语大学者谓之不言存养。而就动处教人则可。论正心者或谓之专主乎体。或谓之专主乎用则不可。故朱子论诚正两条。有曰意是指发处。心是指体言。意是动。心该动静。此岂非端的之论。而果可以偏属体偏属用乎。(按心经讲录。亦以专以用言者为得。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4H 页
 恐愚见终有透不到处。然亦不敢强意以从。当更商之耳。)
恐愚见终有透不到处。然亦不敢强意以从。当更商之耳。)庐院讲会问答劄略(辛卯○所庵李先生主训席)
柳致孝读太极图说。岱镇问各具一太极统体一太极。似有分别。丈席曰太极有二乎。岱镇曰太极非有二。而似有气质本然之别。丈席曰不然。徐更思之。
有问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子作如何看。曰当作阴阳动静离合看。同余说者柳致皓,柳衡镇。丈席及柳致孝,柳圣文皆作理气离合说。后岱镇亦从理气说。
有问妙合之妙如何看。丈席曰且各说所见。岱镇曰恐只是神妙灵妙之妙。盖有运用不测之意。丈席曰只如是。因言理气本自妙合。但说向生物处。较有精彩。
岱镇问善恶者。男女之分。终不能无疑。盖阴阳男女。本自太极生出两个。少一不得。而若善恶则天理中本有善而无恶。未尝对立而并出。若以善恶为男女之象。则善不必为贵而恶亦在所当为也。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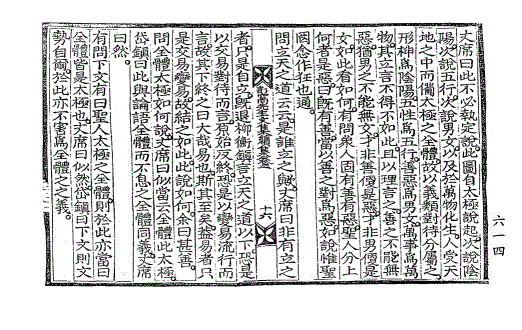 丈席曰此不必执定说。此图自太极说起。次说阴阳。次说五行。次说男女。以及于万物化生。人受天地之中而备太极之全体。故以义类对待分属之。形神为阴阳。五性为五行。善恶为男女。万事为万物。其立言不得不如此。且以理言之。善之不能无恶。犹男之不能无女。才非善便是恶。才非男便是女。如此看如何。有问众人固有善有恶。圣人分上何者是恶。曰既有善。当以善之对为恶。如说惟圣罔念作狂也通。
丈席曰此不必执定说。此图自太极说起。次说阴阳。次说五行。次说男女。以及于万物化生。人受天地之中而备太极之全体。故以义类对待分属之。形神为阴阳。五性为五行。善恶为男女。万事为万物。其立言不得不如此。且以理言之。善之不能无恶。犹男之不能无女。才非善便是恶。才非男便是女。如此看如何。有问众人固有善有恶。圣人分上何者是恶。曰既有善。当以善之对为恶。如说惟圣罔念作狂也通。问立天之道云云。是谁立之欤。丈席曰非有立之者。只是自立。既退柳衡镇言立天之道以下。恐是以交易对待而言。原始反终。恐是以变易流行而言。故其下终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盖易者只是交易变易。故结之如此。此说如何。余曰甚善。
问全体太极如何说。丈席曰似当云全体此太极。岱镇曰此与论语全体而不息之全体同义。丈席曰然。
有问下文有曰圣人太极之全体。则于此亦当曰全体皆是太极也。丈席曰似然。岱镇曰下文则文势自尔。于此亦不害为全体之之义。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5H 页
 李相圣读近思录为学篇。柳致孝问其本也真而静。与未发而五性具者。似为两层说。丈席曰不然。未发而五性具。即其本之真而静者耳。
李相圣读近思录为学篇。柳致孝问其本也真而静。与未发而五性具者。似为两层说。丈席曰不然。未发而五性具。即其本之真而静者耳。岱镇问凿性之凿。终难说破。盖性本无形。与物之可凿者不同。且物之可凿者。一凿而便缺。若性则虽在既凿之后。苟能养之则便自有本然之全体。初未尝被凿也。丈席曰这个当以梏亡之义看取。不必执滞说。
圣人必不害心疾。丈席曰古人有害洁净病。不害之害字。当以此害字看。犹言患也痛也。问洁净病是何病。丈席曰漱石翁尝于孤云寺问此说所从出。某答云不曾考出。但以字义观之。如丈人之不食僧饭。似亦其病也。柳致皓曰此说见于世说。而其人则忘之。然其为病。果似此类。未闻自古圣贤未有因学而致心疾者。岱镇问朱子之心恙。退老之多疾。似是因学致疾。丈席曰虽二先生亦失其节度。故有此样病。其实则学未尝生病。
读至赵师夏诚几说。丈席曰恶亦诚之动一句。终似可疑。此诚字只当以大学诚于中形于外之诚字看取。岱镇曰以程子善恶皆天理之说推之。此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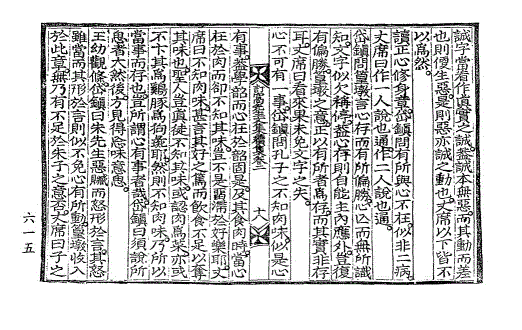 诚字当看作真实之诚。盖诚本无恶。而其动而差也则便生恶。是则恶亦诚之动也。丈席以下皆不以为然。
诚字当看作真实之诚。盖诚本无恶。而其动而差也则便生恶。是则恶亦诚之动也。丈席以下皆不以为然。读正心修身章。岱镇问有所与心不在。似非二病。丈席曰作一人说也通。作二人说也通。
岱镇问篁墩言心存而有所偏胜。心亡而无所识知。文字似欠称停。盖心存则自能主内应外。岂复有偏胜。篁墩之意。正以有所者为存。而其实非存耳。丈席曰看来果未免文字之失。
心不可有一事。岱镇问孔子之不知肉味。似是心有事。盖学韶而心在于韶固是。及其食肉时。当心在于肉而却不知其味。岂不是留滞于好乐耶。丈席曰不知肉味。甚言其好之笃而饮食不足以夺其味也。圣人岂真徒不知其味。或认肉为菜。亦或不卞其为鸡豚为狗彘耶。然则不知肉味。乃所以当事而存也。岂所谓心有事者哉。岱镇曰须说所思者大然后。方见得忘味意思。
王幼观条。岱镇曰朱先生恶赃而怒形于言。其怒虽当而其形于言则似不免心有所动。篁墩收入于此章。无乃有不足于朱子之意否。丈席曰子之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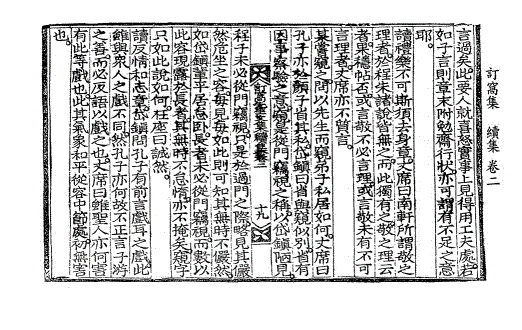 言过矣。此要人就喜怒实事上见得用工夫处。若如子言则章末附勉斋行状。亦可谓有不足之意耶。
言过矣。此要人就喜怒实事上见得用工夫处。若如子言则章末附勉斋行状。亦可谓有不足之意耶。读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章。丈席曰南轩所谓敬之理者。于程朱诸说皆无之。而此独有之。敬之理云者。果稳帖否。或言敬不必言理。或言敬未有不可言理者。丈席亦不质言。
某尝窥之。问以先生而窥弟子私居如何。丈席曰孔子亦于颜子省其私。岱镇曰省与窥似别。省有因事察验之意。窥是从门窃视之称。以岱镇陋见。程子未必从门窃视。只是于过门之际。略见其俨然危坐之容。每见每如此则可知其无时不俨然。如岱镇辈平居怠卧。长者未必从门窃视。而数以此容现露于长者。其无时不怠惰。亦不掩矣。窥字只如此说如何。在座曰诚然。
读反情和志章。岱镇问孔子有前言戏耳之戏。此虽与众人之戏不同。然孔子亦何故不正言子游之善。而必反语以戏之也。丈席曰虽圣人亦何害有此等戏也。此其气象和平从容中节处。初无害也。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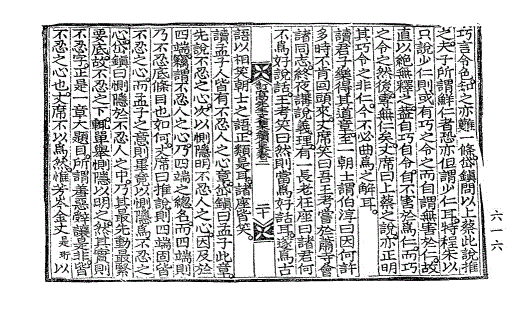 巧言令色。知之亦难一条。岱镇问以上蔡此说推之。夫子所谓鲜仁者恐亦但谓少仁耳。特程朱以只说少仁则或有巧之令之而自谓无害于仁。故直以绝无释之。盖自巧自令。自不害于为仁。而巧之令之然后。专无仁矣。丈席曰上蔡之说。亦正明其巧令之非仁。今不必曲为之解耳。
巧言令色。知之亦难一条。岱镇问以上蔡此说推之。夫子所谓鲜仁者恐亦但谓少仁耳。特程朱以只说少仁则或有巧之令之而自谓无害于仁。故直以绝无释之。盖自巧自令。自不害于为仁。而巧之令之然后。专无仁矣。丈席曰上蔡之说。亦正明其巧令之非仁。今不必曲为之解耳。读君子乐得其道章。至一朝士谓伯淳曰因何许多时不肯回头来。丈席笑曰吾王考尝于萧寺会诸同志。终夜讲说义理。有一长老在座曰诸君何不为好说话。王考笑曰然则当为好话耳。遂为古语以相笑。朝士之语。正类是耳。诸座皆笑。
读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岱镇曰孟子此章。先说不忍之心。次以恻隐明不忍人之心。因及于四端。窃谓不忍人之心。乃四端之总名。而四端则乃不忍底条目也如何。丈席曰推说则四端固皆不忍之心。而孟子之意则毕竟以恻隐为不忍之心。岱镇曰恻隐于不忍人之中。乃其最先动最紧要底。故不忍之下。辄单举恻隐以明之。然其实则不忍字。正是一章大题目。所谓羞恶辞让是非。皆不忍之心也。丈席不以为然。惟芳岑金丈(是珩)以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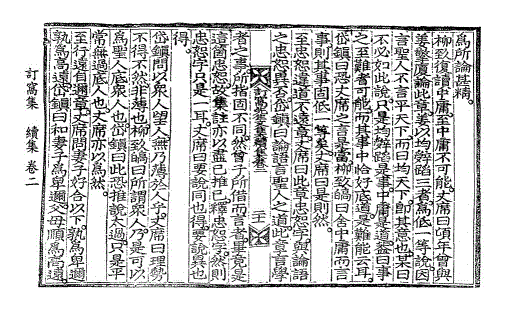 为所论甚精。
为所论甚精。柳致复读中庸。至中庸不可能。丈席曰顷年曾与姜擎厦论此章。姜以均辞蹈三者。为低一等说。因言圣人不言平天下。而曰均天下。即其意也。某曰不必如此说。只是均辞蹈是事。中庸是道。盖曰事之至难者可能。而其事中恰好底道。是难能云耳。岱镇曰恐丈席之言是当。柳致皓曰舍中庸而言事。则其事固低一等矣。丈席曰是则然。
至忠恕违道不远章。丈席曰此章忠恕字。与论语之忠恕异否。岱镇曰论语言圣人之道。此章言学者之事。所指固不同。然曾子所借而言者。毕竟是这个忠恕。故集注亦以尽己推己。释忠恕字。然则忠恕字只是一耳。丈席曰要说同也得。要说异也得。
岱镇问以众人望人。无乃薄于人乎。丈席曰理势不得不然。非薄也。柳致皓曰所谓众人。乃是可以为圣人底众人也。岱镇曰此恐推说太过。只是平常无过底人也。丈席亦以为然。
至行远自迩章。丈席问妻子好合以下。孰为卑迩孰为高远。岱镇曰和妻子为卑迩。父母顺为高远。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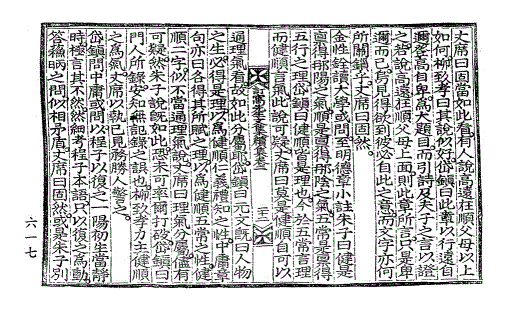 丈席曰固当如此看。有人说高远在顺父母以上如何。柳致孝曰其说似好。岱镇曰此章以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为大题目。而引诗及夫子之言以證之。若说高远在顺父母上面。则此章所言。只是卑迩而已。乌见得欲到彼必自此之意。而文字亦何所关锁乎。丈席曰固然。
丈席曰固当如此看。有人说高远在顺父母以上如何。柳致孝曰其说似好。岱镇曰此章以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为大题目。而引诗及夫子之言以證之。若说高远在顺父母上面。则此章所言。只是卑迩而已。乌见得欲到彼必自此之意。而文字亦何所关锁乎。丈席曰固然。金性铨读大学或问。至明德章小注朱子曰健是禀得那阳之气。顺是禀得那阴之气。五常是禀得五行之理。岱镇曰健顺皆是理也。今于五常言理而健顺言气。此说可疑。丈席曰莫是健顺自可以通理气看。故如此分属耶。岱镇曰元文既曰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为健顺仁义礼知之性。中庸章句亦曰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性。健顺二字。似不当通理气说。丈席曰理气分属。尽有可疑。然朱子说既如此。恐未可率尔打破。岱镇曰门人所录。安知无记录之误也。柳致孝力主健顺之为气。丈席以执己见务胜人警之。
岱镇问中庸或问。以程子以复之一阳初生当静时。极言其不然。然细考程子本语。只以复之为动。答苏炳之问。似相矛盾。丈席曰固然。或是朱子别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8H 页
 有所据欤。未可知也。
有所据欤。未可知也。岱镇问中庸章句所得之理既尽云者。小注释以澌尽终似有病。丈席曰王考已言其非矣。岱镇曰寻常以理尽物尽为疑。盖尝反复思之。凡一物之理。自有始此物底。自有终此物底。其终此物底。便是理之尽处。这尽字恰似说起止一般。丈席曰然。
有问孟子浩然章两馁字。岱镇曰无是馁也。是指道义而言。行有不慊于心则馁。是指气而言。丈席曰道义著馁字不得。无论上下馁字。皆当言体不充。
丈席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节。只是大纲说。凡物如此。凡事如此。当知其所当先所当后云尔。非的指明新与知得也。但其意以明新知得。当以此例通也。岱镇曰此说甚当。或曰章句既以明新知得。释本末先后。恐未可如此泛说。岱镇曰试观章句之释。不曰本指明德末指新民云云。而曰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云云。其意亦似以此章为大纲说。而将明新知得类属之耳。丈席曰然。
岱镇问四德之知与知觉之知。当有分别。丈席曰不是两知也。只四德之知为体。而知觉之知为用。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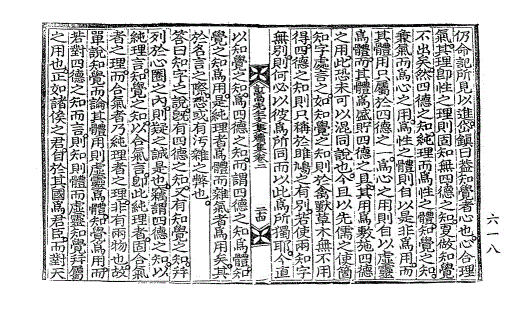 仍命记所见以进。岱镇曰盖知觉者心也。心合理气。其理即性之理则固知无四德之知。更做知觉不出矣。然四德之知。纯理而为性之体。知觉之知。兼气而为心之用。为性之体则自以是非为用。而其体用只属于四德之一。为心之用则自以虚灵为体。而其体为盛贮四德之具。其用为敷施四德之用。此恐未可以混同说也。今且以先儒之使个知字处言之。如知觉之知则于禽兽草木无不用得。四德之知则只称于雎鸠之有别。若使两知字无别。则何必以彼为所同而以此为所独耶。今直以知觉之知。为四德之知。而谓四德之知为体。知觉之知为用。是纯理者为体而杂气者为用矣。其于名言之际。恐或有污杂之弊也。
仍命记所见以进。岱镇曰盖知觉者心也。心合理气。其理即性之理则固知无四德之知。更做知觉不出矣。然四德之知。纯理而为性之体。知觉之知。兼气而为心之用。为性之体则自以是非为用。而其体用只属于四德之一。为心之用则自以虚灵为体。而其体为盛贮四德之具。其用为敷施四德之用。此恐未可以混同说也。今且以先儒之使个知字处言之。如知觉之知则于禽兽草木无不用得。四德之知则只称于雎鸠之有别。若使两知字无别。则何必以彼为所同而以此为所独耶。今直以知觉之知。为四德之知。而谓四德之知为体。知觉之知为用。是纯理者为体而杂气者为用矣。其于名言之际。恐或有污杂之弊也。答曰知字之说。既有四德之知。又有知觉之知。并列于心圈之内。则疑之诚是也。窃谓四德之知。以纯理言。知觉之知。以合气言。即此纯理者。固合气者之理。而合气者乃纯理者之理。非有两物也。故单说知觉而论其体用则虚灵为体。知觉为用。而若对四德之知而言。则知则体而虚灵知觉并属之用也。正如诸侯之君。自于其国为君臣。而对天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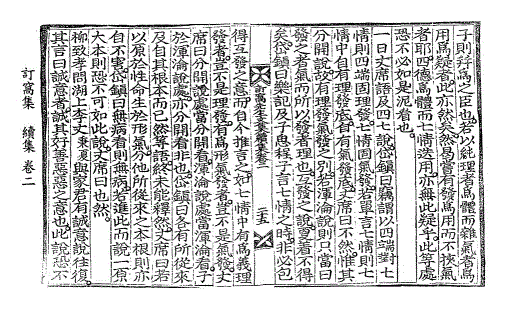 子则并为之臣也。若以纯理者为体而杂气者为用为疑者。此亦然矣。然曷尝有发为用而不挟气者耶。四德为体而七情迭用。亦无此疑乎。此等处恐不必如是泥看也。
子则并为之臣也。若以纯理者为体而杂气者为用为疑者。此亦然矣。然曷尝有发为用而不挟气者耶。四德为体而七情迭用。亦无此疑乎。此等处恐不必如是泥看也。一日丈席语及四七说。岱镇曰窃谓以四端对七情则四端固理发。七情固气发。若单言七情则七情中自有理发底。自有气发底。丈席曰不然。惟其分开说。故有理发气发之别。若浑沦说则只当曰发之者气而所以发者理也。互发之说。更着不得矣。岱镇曰乐记及子思程子言七情之时。非必包得互发之意。而自今推言之。如七情中有为义理发者。岂不是理发。有为形气发者。岂不是气发。丈席曰分开说处当分开看。浑沦说处当浑沦看。子于浑沦说处。亦分开看非也。岱镇曰各有所从来及自其根本而已然等语。终未能释然。丈席曰若以原于性命生于形气。分他所从来之本根则亦自不害。岱镇曰无病看则无病。若进此而说一原大本则恐不可如此说。丈席曰也然。
柳致孝问湖上李丈(秉夏)与家君有诚意说往复。其言曰诚意者。诚其好善恶恶之意也。此说恐不
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19L 页
 可易。若以这意字兼善恶说则恶亦可诚乎。丈席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心之所发。自有许多般样。今以此意字只作好善恶恶意看。语巧而意偏。不可从也。于是辩论纷然。然到恶亦可诚之文。往往语窒而窘。其说有数般。或曰诚意之诚字。自兼得实为善实去恶之意。故意虽有善有恶。而自无恶亦可诚之意。(柳圣文说。)或曰诚意在致知之后。故意虽有善有恶。而所诚者必在于善。(柳致皓,金▼(铁-戈+攴)说。)岱镇亦周旋于数说之间。反复思之。许多所说。终归于好善恶恶上。盖意固有善恶矣。有好恶矣。但于诚之之际。以此好恶。择此善恶。以实为善而实去恶。则所诚之意。岂不是好善而恶恶者乎。丈席命诸生各记所见以进。岱镇曰诚意者。不过曰诚其好善恶恶之意也。盖好善恶恶。非可以训意字。而诚意之意。舍好善恶恶字说不得矣。难此说者曰意自有善恶有好恶。今只归之善一边则非意字本面目。此固然矣。然以意为好善恶恶之意者。亦曰以此好好此善。以此恶恶此恶。则何尝与意字本面相反耶。难者又曰诚意上面。已有致知工夫。故这意字只作有善有恶之意。而自无恶亦可
可易。若以这意字兼善恶说则恶亦可诚乎。丈席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心之所发。自有许多般样。今以此意字只作好善恶恶意看。语巧而意偏。不可从也。于是辩论纷然。然到恶亦可诚之文。往往语窒而窘。其说有数般。或曰诚意之诚字。自兼得实为善实去恶之意。故意虽有善有恶。而自无恶亦可诚之意。(柳圣文说。)或曰诚意在致知之后。故意虽有善有恶。而所诚者必在于善。(柳致皓,金▼(铁-戈+攴)说。)岱镇亦周旋于数说之间。反复思之。许多所说。终归于好善恶恶上。盖意固有善恶矣。有好恶矣。但于诚之之际。以此好恶。择此善恶。以实为善而实去恶。则所诚之意。岂不是好善而恶恶者乎。丈席命诸生各记所见以进。岱镇曰诚意者。不过曰诚其好善恶恶之意也。盖好善恶恶。非可以训意字。而诚意之意。舍好善恶恶字说不得矣。难此说者曰意自有善恶有好恶。今只归之善一边则非意字本面目。此固然矣。然以意为好善恶恶之意者。亦曰以此好好此善。以此恶恶此恶。则何尝与意字本面相反耶。难者又曰诚意上面。已有致知工夫。故这意字只作有善有恶之意。而自无恶亦可订窝先生文集续集卷之二 第 620H 页
 诚之疑。又曰诚之一字。自兼得实为善实去恶之意。故这意字亦作有善有恶之意而亦无恶亦可诚之疑。此亦然矣。然知为善以去恶。而实为善实去恶。则其意也亦何尝不归于好善恶恶上耶。是则上面之有致知工夫。诚字之兼两端工夫者。正所以发明意字之为好善恶恶也。安得执此而攻彼耶。
诚之疑。又曰诚之一字。自兼得实为善实去恶之意。故这意字亦作有善有恶之意而亦无恶亦可诚之疑。此亦然矣。然知为善以去恶。而实为善实去恶。则其意也亦何尝不归于好善恶恶上耶。是则上面之有致知工夫。诚字之兼两端工夫者。正所以发明意字之为好善恶恶也。安得执此而攻彼耶。丈席辩曰诚意说。众说交互。不可典要。窃意此章意字。所包甚广。情虑志思。总脑于一个意字。则善恶之几。好恶之端。皆是意也。意之为字。本以经营料度而得名。则经营料度者。岂可独言于一段好恶。而不得说于心之所发善恶之几耶。今只说善恶而以好恶归之致知者。固为偏而不活。而只归好恶而不得犯涉善恶者。亦恐缓而不切。至于虚看意字者。又似茫荡。盖以此章则承以毋自欺以下工夫。虽无空同之嫌。而经文诚意。其无交涉甚矣。今且权倚阁意是甚情是甚。只就心之发处。实下诚之之工。则方见得诚意意味。不须如此作一场閒争竞。未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