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x 页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杂著
杂著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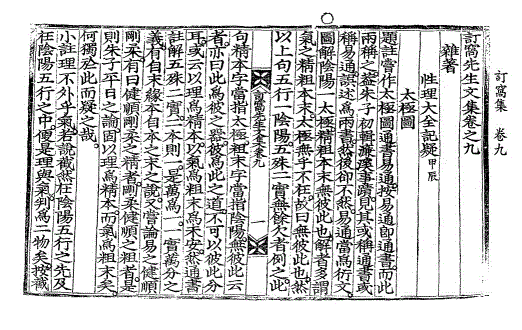 性理大全记疑(甲辰)
性理大全记疑(甲辰)太极图
题注尝作太极图通书易通。按易通即通书。而此两称之。盖朱子初辑濂溪事迹。见其或称通书或称易通。误述为两书。然后却不然。易通当为衍文。
图解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解者多谓气之精粗本末。太极无乎不在。故曰无彼此也。然以上句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馀欠者例之。此句精本字当指太极。粗末字当指阴阳。无彼此云者。亦曰此为彼之器。彼为此之道。不可以彼此分耳。或云以理为精本。以气为粗末为未安。然通书注解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之义。有自末缘本自本之末之说。又尝论易之健顺刚柔。有曰健顺刚柔之精者。刚柔健顺之粗者。是则朱子平日之论。固以理为精本。而气为粗末矣。何独于此而疑之哉。
小注理不外乎气。若说截然在阴阳五行之先及在阴阳五行之中。便是理与气。判为二物矣。按截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8L 页
 然字有病故云然。然理与气。谓之非二物亦不可。
然字有病故云然。然理与气。谓之非二物亦不可。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即太极之静。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生此阴阳之气。谓之动而生静而生则有渐次也。按此一条。与所谓不是动后方生阳。才动便属阳。才静便属阴者不同。当各做一义看。盖动静即阴阳。不是动静外别生阴阳。然推其动静之所以然。则阳乃太极之动而生者也。阴乃太极之静而生者也。故曰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盖曰有理而后有气。即所谓有渐次者也。然亦非谓今日有理而明日有气。特就其所以然处。分个先后耳。
太极自是函动静之理。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盖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按静为太极之体。动为太极之用。则其曰不可以动静分体用者何也。盖太极函动静。静即体动即用。然其动底即其静底。其静底即其动底。不可将动静作对立两端看。以为此是体彼是用也。
气质之性。只是此理堕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周子所谓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气质之性。从何处得来。按此气质本然之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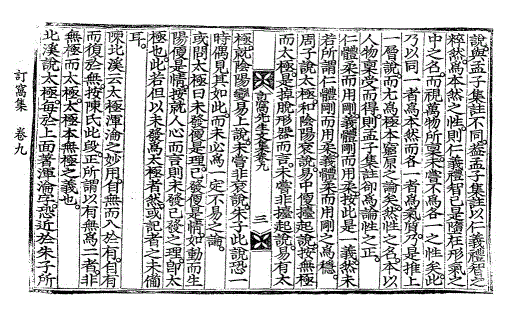 说。与孟子集注不同。盖孟子集注以仁义礼智之粹然。为本然之性。则仁义礼智已是堕在形气之中之名。而视万物所禀。未尝不为各一之性矣。此乃以同一者为本然而各一者为气质。乃是推上一层说。而尤为极本穷原之论矣。然性之名。本以人物禀受而得。则孟子集注却为论性之正。
说。与孟子集注不同。盖孟子集注以仁义礼智之粹然。为本然之性。则仁义礼智已是堕在形气之中之名。而视万物所禀。未尝不为各一之性矣。此乃以同一者为本然而各一者为气质。乃是推上一层说。而尤为极本穷原之论矣。然性之名。本以人物禀受而得。则孟子集注却为论性之正。仁体柔而用刚。义体刚而用柔。按此是一义。然未若所谓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之为稳。
周子说太极。和阴阳衮说。易中便抬起说。按无极而太极。是掉脱形器而言。未尝非抬起说。易有太极。就阴阳变易上说。未尝非衮说。朱子此说恐一时偶见其如此。而未必为一定不易之论。
或问太极曰未发便是理。已发便是情。如动而生阳便是情。按就人心而言则未发已发之理。即太极也。此若但以未发为太极者然。或记者之未备耳。
陈北溪云太极浑沦之妙用。自无而入于有。自有而复于无。按陈氏此段。正所谓以有无为二者。非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之义也。
北溪说太极。每于上面著浑沦字。恐近于朱子所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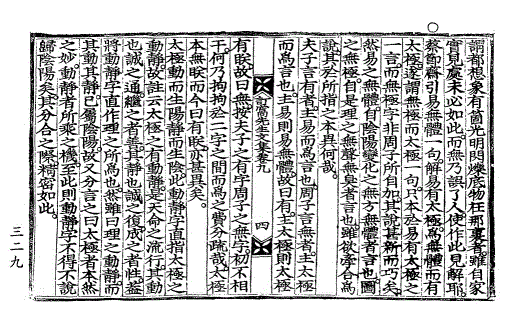 谓都想象有个光明闪烁底物在那里者。虽自家实见处未必如此。而无乃误了人。使作此见解耶。
谓都想象有个光明闪烁底物在那里者。虽自家实见处未必如此。而无乃误了人。使作此见解耶。蔡节斋引易无体一句。解易有太极。为无体而有太极。遂谓无极而太极一句。只本于易有太极之一言。而无极字非周子所自加。其说甚新而巧矣。然易之无体。自阴阳变化之无方无体者言也。图之无极。自是理之无声无臭者言也。虽欲牵合为说。其于所指之本异何哉。
夫子言有者。主易而为言也。周子言无者。主太极而为言也。主易则易无体。故曰有。主太极则太极有眹。故曰无。按夫子之有字周子之无字。初不相干。何乃拘拘于二字之间而为之费分疏哉。太极本无眹而今曰有眹。亦甚异矣。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此动静字直指太极之动静。故注云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其动也诚之通。继之者善。其静也诚之复。成之者性。盖将动静字直作理之所为也。然虽曰理之动静。而其动其静。已属阴阳。故又分言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至此则动静字不得不说归阴阳矣。其分合之际。精密如此。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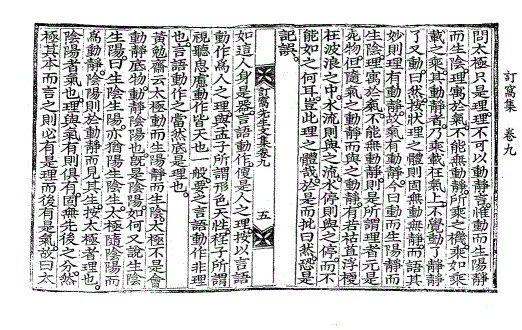 问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所乘之机。乘如乘载之乘。其动静者。乃乘载在气上。不觉动了静静了又动。曰然。按状理之体则固无动无静。而语其妙则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今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则是所谓理者元是死物。但随气之动静而与之动静。有若枯苴浮梗在波浪之中。水流则与之流。水停则与之停。而不能如之何耳。岂此理之体哉。于是而批曰然。恐是记误。
问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所乘之机。乘如乘载之乘。其动静者。乃乘载在气上。不觉动了静静了又动。曰然。按状理之体则固无动无静。而语其妙则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今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则是所谓理者元是死物。但随气之动静而与之动静。有若枯苴浮梗在波浪之中。水流则与之流。水停则与之停。而不能如之何耳。岂此理之体哉。于是而批曰然。恐是记误。如这人身是器。言语动作。便是人之理。按以言语动作为人之理。与孟子所谓形色天性。程子所谓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一般。要之言语动作非理也。言语动作之当然底是理也。
黄勉斋云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太极不是会动静底物。动静阴阳也。既是阴阳。如何又说生阴生阳。曰生阴生阳。亦犹阳生阴生。太极随阴阳而为动静。阴阳则于动静而见其生。按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理与气有则俱有。固无先后之分。然极其本而言之则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故曰太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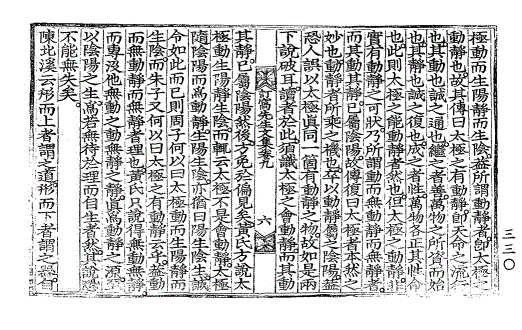 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盖所谓动静者。即太极之动静也。故其传曰太极之有动静。即天命之流行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而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此则太极之能动静者然也。但太极之动静。非实有动静之可状。乃所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者。而其动其静。已属阴阳。故传复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卒以动静属之阴阳。盖恐人误以太极真同一个有动静之物。故如是两下说破耳。读者于此。须识太极之会动静。而其动其静。已属阴阳然后。方免于偏见矣。黄氏方说太极动生阳静生阴。而辄云太极不是会动静。太极随阴阳而为动静。生阳生阴。亦犹曰阳生阴生。诚令如此而已则周子何以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而朱子又何以曰太极之有动静云乎。盖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者理也。黄氏只说得无动无静。而专没他无动之动无静之静。真为动静之源。至以阴阳之生。为若无待于理而自生者然。其说恐不能无失矣。
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盖所谓动静者。即太极之动静也。故其传曰太极之有动静。即天命之流行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而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此则太极之能动静者然也。但太极之动静。非实有动静之可状。乃所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者。而其动其静。已属阴阳。故传复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卒以动静属之阴阳。盖恐人误以太极真同一个有动静之物。故如是两下说破耳。读者于此。须识太极之会动静。而其动其静。已属阴阳然后。方免于偏见矣。黄氏方说太极动生阳静生阴。而辄云太极不是会动静。太极随阴阳而为动静。生阳生阴。亦犹曰阳生阴生。诚令如此而已则周子何以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而朱子又何以曰太极之有动静云乎。盖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者理也。黄氏只说得无动无静。而专没他无动之动无静之静。真为动静之源。至以阴阳之生。为若无待于理而自生者然。其说恐不能无失矣。陈北溪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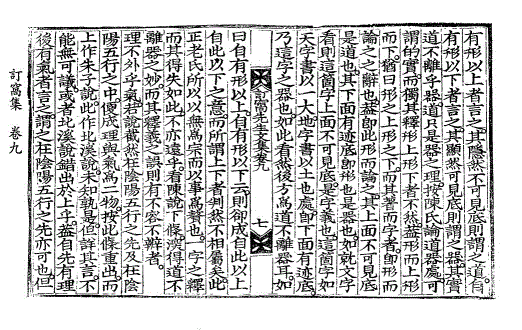 有形以上者言之。其隐然不可见底则谓之道。自有形以下者言之。其显然可见底则谓之器。其实道不离乎器。道只是器之理。按陈氏论道器处。可谓的实。而独其释形上形下者不然。盖形而上形而下。犹曰形之上形之下。而其著而字者。即形而论之之辞也。盖即此形而论之。其上面不可见底是道也。其下面有迹底即形也是器也。如就文字看则这个字上面不可见底。是字义也。这个字如天字书以一大。地字书以土也处。即下面有迹底。乃这字之器也。如此看然后方为道不离器耳。如曰自有形以上。自有形以下云。则却成自此以上自此以下之意。而所谓上下者判然不相属矣。此正老氏所以以无为宗而以事为赘也。一字之释而其得失如此。不亦远乎。看陈说下条。深得道不离器之妙。而其释义之误则有不容不辨者。
有形以上者言之。其隐然不可见底则谓之道。自有形以下者言之。其显然可见底则谓之器。其实道不离乎器。道只是器之理。按陈氏论道器处。可谓的实。而独其释形上形下者不然。盖形而上形而下。犹曰形之上形之下。而其著而字者。即形而论之之辞也。盖即此形而论之。其上面不可见底是道也。其下面有迹底即形也是器也。如就文字看则这个字上面不可见底。是字义也。这个字如天字书以一大。地字书以土也处。即下面有迹底。乃这字之器也。如此看然后方为道不离器耳。如曰自有形以上。自有形以下云。则却成自此以上自此以下之意。而所谓上下者判然不相属矣。此正老氏所以以无为宗而以事为赘也。一字之释而其得失如此。不亦远乎。看陈说下条。深得道不离器之妙。而其释义之误则有不容不辨者。理不外乎气。若说截然在阴阳五行之先及在阴阳五行之中。便成理与气为二物。按此条重出。而上作朱子说。此作北溪说。未知孰是。但详其言。不能无可议。或者北溪说错出于上乎。盖自先有理后有气者言之。谓之在阴阳五行之先亦可也。但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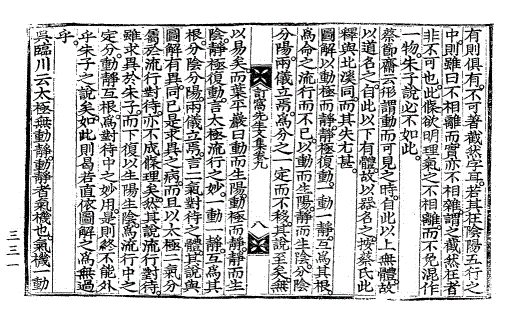 有则俱有。不可著截然字耳。若其在阴阳五行之中。则虽曰不相离而实亦不相杂。谓之截然在者非不可也。此条欲明理气之不相离。而不免混作一物。朱子说必不如此。
有则俱有。不可著截然字耳。若其在阴阳五行之中。则虽曰不相离而实亦不相杂。谓之截然在者非不可也。此条欲明理气之不相离。而不免混作一物。朱子说必不如此。蔡节斋云形谓动而可见之时。自此以上无体。故以道名之。自此以下有体。故以器名之。按蔡氏此释与北溪同。而其失尤甚。
图解以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为命之流行而不已。以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为分之一定而不移。其说至矣。无以易矣。而叶平岩曰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言太极流行之妙。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言二气对待之体。其说与图解有异。同已是求异之病。而且以太极二气分属于流行对待。亦不成条理矣。然其说流行对待。虽求异于朱子。而下复以生阳生阴。为流行中之定分。动静互根。为对待中之妙用。是则终不能外乎朱子之说矣。如此则曷若直依图解之为无过乎。
吴临川云太极无动静。动静者气机也。气机一动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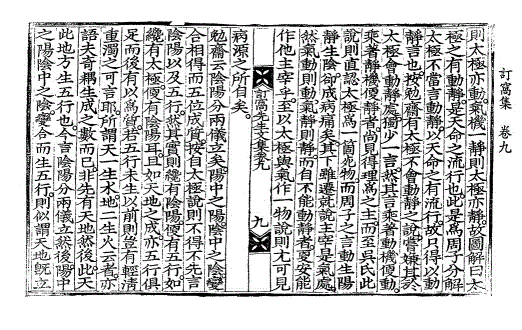 则太极亦动。气机一静则太极亦静。故图解曰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为周子分解太极不当言动静。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动静言也。按勉斋有太极不会动静之说。尝嫌其于太极会动静处。独少一言。然其言乘著动机便动。乘著静机便静者。尚见得理为之主。而至吴氏此说则直认太极为一个死物。而周子之言动生阳静生阴。却成病痛矣。其下虽迁就说主宰是气处。然气动则动。气静则静。而自不能动静者。更安能作他主宰乎。至以太极与气作一物说则尤可见病源之所自矣。
则太极亦动。气机一静则太极亦静。故图解曰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为周子分解太极不当言动静。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动静言也。按勉斋有太极不会动静之说。尝嫌其于太极会动静处。独少一言。然其言乘著动机便动。乘著静机便静者。尚见得理为之主。而至吴氏此说则直认太极为一个死物。而周子之言动生阳静生阴。却成病痛矣。其下虽迁就说主宰是气处。然气动则动。气静则静。而自不能动静者。更安能作他主宰乎。至以太极与气作一物说则尤可见病源之所自矣。勉斋云阴阳分两仪立矣。阳中之阳。阴中之阴。变合相得而五位成质。按自太极说则不得不先言阴阳以及五行。然其实则才有阴阳。便有五行。如才有太极。便有阴阳耳。且如天地之成。亦五行俱足而后有以为质。若五行未生以前则岂有轻清重浊之可言耶。所谓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云者。亦语夫奇耦生成之数而已。非先有天地然后。此天此地方生五行也。今言阴阳分两仪立然后。阳中之阳阴中之阴。变合而生五行。则似谓天地既立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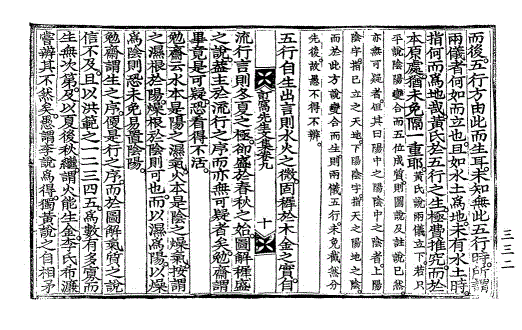 而后。五行方由此而生耳。未知无此五行时。所谓两仪者何如而立也。且如水土为地。未有水土时。指何而为地哉。黄氏于五行之生。极费推究。而于本原处。犹未免隔一重耶。(黄氏说两仪立下。若只平说阴阳变合而五位成质。则图说及注说已然。亦无可疑者。但其曰阳中之阳阴中之阴者。上阳阴字。指已立之天地。下阳阴字。指天之阳地之阴。而于此方说变合而生。则两仪五行。未免截然分先后。故愚不得不辨。)
而后。五行方由此而生耳。未知无此五行时。所谓两仪者何如而立也。且如水土为地。未有水土时。指何而为地哉。黄氏于五行之生。极费推究。而于本原处。犹未免隔一重耶。(黄氏说两仪立下。若只平说阴阳变合而五位成质。则图说及注说已然。亦无可疑者。但其曰阳中之阳阴中之阴者。上阳阴字。指已立之天地。下阳阴字。指天之阳地之阴。而于此方说变合而生。则两仪五行。未免截然分先后。故愚不得不辨。)五行自生出言则水火之微。固稚于木金之实。自流行言则冬夏之极。却盛于春秋之始。图解稚盛之说。盖主于流行之序而亦无可疑者矣。勉斋谓毕竟是可疑。恐看得不活。
勉斋云水本是阳之湿气。火本是阴之燥气。按谓之湿根于阳。燥根于阴则可也。而以湿为阳。以燥为阴则恐未免易置阴阳。
勉斋谓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于图解气质之说信不及。且以洪范之一二三四五。为数有多寡而生无次第。及以夏后秋继。谓火能生金。李氏希濂尝辨其不然矣。愚谓李说为得。独黄说之自相矛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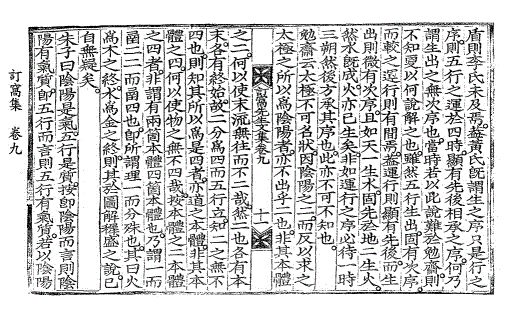 盾则李氏未及焉。盖黄氏既谓生之序只是行之序。则五行之运于四时。显有先后相承之序。何乃谓生出之无次序也。当时若以此说难于勉斋。则不知更以何说解之也。虽然五行生出。固有次序。而较之运行则有间焉。盖运行则显有先后。而生出则微有次序。且如天一生水。固先于地二生火。然水既成。火亦已生矣。非如运行之序必待一时三朔然后方承其序也。此亦不可不知也。
盾则李氏未及焉。盖黄氏既谓生之序只是行之序。则五行之运于四时。显有先后相承之序。何乃谓生出之无次序也。当时若以此说难于勉斋。则不知更以何说解之也。虽然五行生出。固有次序。而较之运行则有间焉。盖运行则显有先后。而生出则微有次序。且如天一生水。固先于地二生火。然水既成。火亦已生矣。非如运行之序必待一时三朔然后方承其序也。此亦不可不知也。勉斋云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极之所以为阴阳者。亦不出乎二也。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而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终始。故二分为四而五行立。知二之无不四也。则知其所以为是四者。亦道之本体。非其本体之四。何以使物之无不四哉。按本体之二本体之四者。非谓有两个本体四个本体也。乃谓一而函二二而函四也。即所谓理一而分殊也。其曰火为木之终。水为金之终。则其于图解稚盛之说。已自无疑矣。
朱子曰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按即阴阳而言则阴阳有气质。即五行而言则五行有气质。若以阴阳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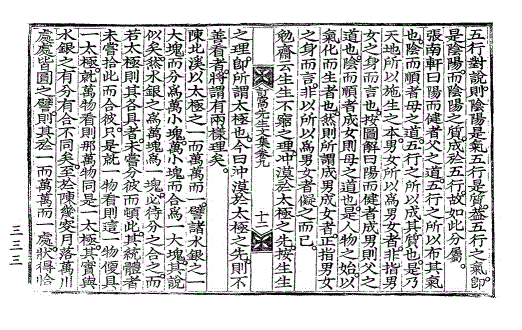 五行对说。则阴阳是气五行是质。盖五行之气。即是阴阳。而阴阳之质。成于五行。故如此分属。
五行对说。则阴阳是气五行是质。盖五行之气。即是阴阳。而阴阳之质。成于五行。故如此分属。张南轩曰阳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气也。阴而顺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质也。是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为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也。按图解曰阳而健者成男则父之道也。阴而顺者成女则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然则所谓成男成女者。正指男女之身而言。非以所以为男女者儗之而已。
勉斋云生生不穷之理。冲漠于太极之先。按生生之理。即所谓太极也。今曰冲漠于太极之先。则不善看者。将谓有两样理矣。
陈北溪以太极之一而万万而一。譬诸水银之一大块而分为万小块。万小块而合为一大块。其说似矣。然水银之为万块为一块。必待分之合之。而若太极则其各具者。未尝分彼而顿此。其统体者未尝拾此而合彼。只是就一物看则这一物便具一太极。就万物看则那万物同是一太极。其实与水银之有分有合不同矣。至于陈几叟月落万川处处皆圆之譬。则其于一而万万而一处。状得恰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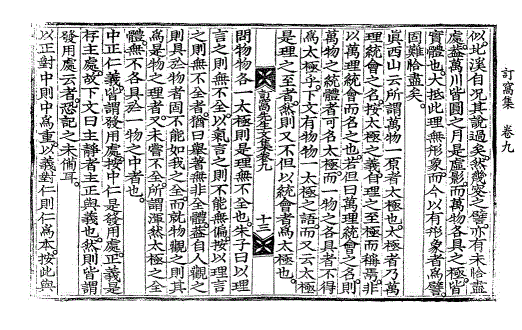 似。北溪自况其说过矣。然几叟之譬。亦有未恰尽处。盖万川皆圆之月是虚影。而万物各具之极。皆实体也。大抵此理无形象。而今以有形象者为譬。固难恰尽矣。
似。北溪自况其说过矣。然几叟之譬。亦有未恰尽处。盖万川皆圆之月是虚影。而万物各具之极。皆实体也。大抵此理无形象。而今以有形象者为譬。固难恰尽矣。真西山云所谓万物一原者太极也。太极者乃万理统会之名。按太极之义。自理之至极而称焉。非以万理统会而名之也。若但曰万理统会之名。则万物之统体者可名太极。而一物之各具者不得为太极乎。下文有物物一太极之语。而又云太极是理之至者。然则又不但以统会者为太极也。
问物物各一太极则是理无不全也。朱子曰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按以理言之则无不全者。犹曰举著无非全体。盖自人观之则具于物者固不能如我之全。而就物观之则其为是物之理者。又未尝不全。所谓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者也。
中正仁义。皆谓发用处。按中仁是发用处。正义是存主处。故下文曰主静者主正与义也。然则皆谓发用处云者。恐记之未备耳。
以正对中则中为重。以义对仁则仁为本。按此与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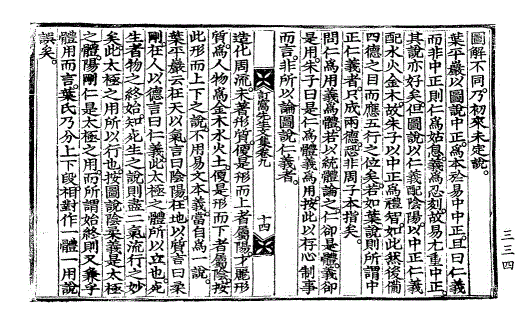 图解不同。乃初来未定说。
图解不同。乃初来未定说。叶平岩以图说中正。为本于易中中正。且曰仁义而非中正则仁为姑息。义为忍刻。故易尤重中正。其说亦好矣。但图说以仁义配阴阳。以中正仁义配水火金木。故朱子以中正为礼智。如此然后备四德之目而应五行之位矣。若如叶说则所谓中正仁义者。只成两德。恐非周子本指矣。
问仁为用义为体。若以统体论之。仁却是体。义却是用。朱子曰是仁为体义为用。按此以存心制事而言。非所以论图说仁义者。
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是形而下者属阴。按此形而上下之说。不用易文本义。当自为一说。
叶平岩云在天以气言曰阴阳。在地以质言曰柔刚。在人以德言曰仁义。此太极之体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终始。知死生之说则尽二气流行之妙矣。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按图说阴柔义是太极之体。阳刚仁是太极之用。而所谓始终则又兼乎体用而言。叶氏乃分上下段。相对作一体一用说误矣。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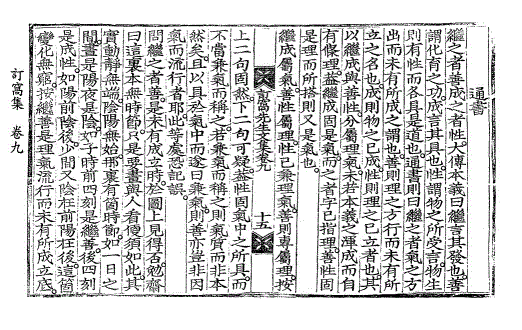 通书
通书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传本义曰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通书则曰继之者气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谓也。善则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成则物之已成。性则理之已立者也。其以继成与善性。分属理气。未若本义之浑成而自有条理。盖继成固是气。而之者字已指理。善性固是理而所搭则又是气也。
继成属气。善性属理。性已兼理气。善则专属理。按上二句固然。下二句可疑。盖性固气中之所具。而不当兼气而称之。若兼气而称之则气质而非本然矣。且以具于气中而遂曰兼气。则善亦岂非因气而流行者耶。此等处恐记误。
问继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时。于图上见得否。勉斋曰这里本无时节。只是要画与人看便须如此。其实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那里有个时节。如一日之间。昼是阳夜是阴。如子时前四刻是继善。后四刻是成性。如阳前阴后。少间又阴在前阳在后。这个变化无穷。按继善是理气流行而未有所成立底。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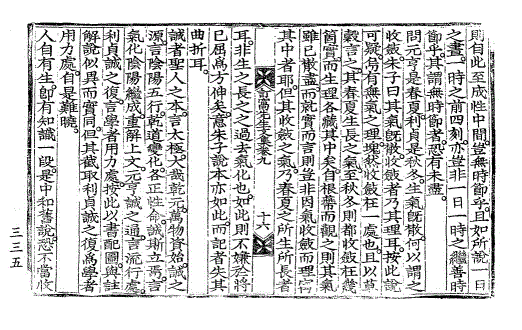 则自此至成性中间。岂无时节乎。且如所说一日之昼。一时之前四刻。亦岂非一日一时之继善时节乎。其谓无时节者。恐有未尽。
则自此至成性中间。岂无时节乎。且如所说一日之昼。一时之前四刻。亦岂非一日一时之继善时节乎。其谓无时节者。恐有未尽。问元亨是春夏。利贞是秋冬。生气既散。何以谓之收敛。朱子曰其气既散。收敛者乃其理耳。按此说可疑。乌有无气之理。块然收敛在一处也。且以草谷言之。其春夏生长之气。至秋冬则都收敛在几个实。而生理各藏其中矣。自根蒂而观之则其气虽已散尽。而就实而言则岂非因气收敛而理寓其中者耶。但其收敛之气。乃春夏之所生所长者耳。非生之长之之过去气化也。如此则不嫌于将已屈为方伸矣。意朱子说本亦如此。而记者失其曲折耳。
诚者圣人之本。言太极。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言阴阳五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言气化阴阳继成。重解上文。元亨诚之通。言流行处。利贞诚之复。言学者用力处。按此以书配图。与注解说似异而实同。但其截取利贞诚之复为学者用力处。自是难晓。
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一段。是中和旧说。恐不当收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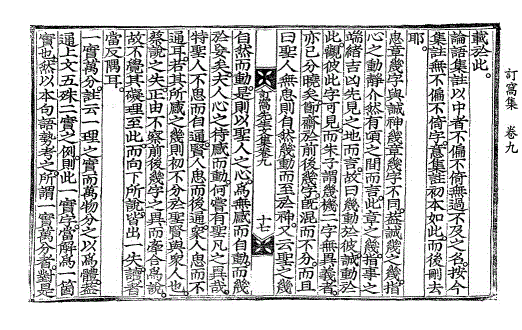 载于此。
载于此。论语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按今集注无不偏不倚字。意集注初本如此。而后删去耶。
思章几字与诚神几章几字不同。盖诚几之几。指心之动静介然有顷之间而言。此章之几。指事之端绪吉凶先见之地而言。故曰几动于彼。诚动于此。观彼此字可见。而朱子谓几机二字无异义者。亦已分晓矣。节斋于前后几字。既混而不分。而且曰圣人无思则自然几动而至于神。又云圣之几自然而动。是则以圣人之心。为无感而自动。而几于妄矣。夫人心之待感而动。何尝有圣凡之异哉。特圣人不思而自通。贤人思而后通。众人思而不通耳。若其所感之几则初不分于圣贤与众人也。蔡说之失。正由不察前后几字之异而牵合为说。故不觉其碍理至此。而向下所说。皆出一失。读者当反隅耳。
一实万分。注云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盖通上文五殊二实之例。则此一实字。当解为一个实也。然以本句语势考之。所谓一实万分者。对是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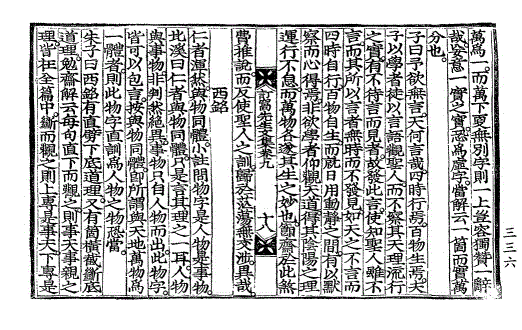 万为一。而万下更无别字则一上岂容独赞一辞哉。妄意一实之实。恐为虚字。当解云一个而实万分也。
万为一。而万下更无别字则一上岂容独赞一辞哉。妄意一实之实。恐为虚字。当解云一个而实万分也。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以学者徒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见者。故发此言。使知圣人虽不言。而其所以言者无时而不发见。如天之不言而四时自行。百物自生。而就日用动静之间。有以默察而心得焉。非欲学者仰观天道。得其阴阳之理运行不息。而万物各遂其生之妙也。节斋于此煞费推说。而反使圣人之训。归于茫荡无交涉。异哉。
西铭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小注问物字是人物是事物。北溪曰仁者与物同体。只是言其理之一耳。人物与事物。非判然绝异。事物只自人物而出。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按与物同体。即所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则此物字直训为人物之物恐当。
朱子曰西铭有直劈下底道理。又有个横截断底道理。勉斋解云每句直下而观之。则事天事亲之理。皆在全篇中。断而观之则上专是事天。下专是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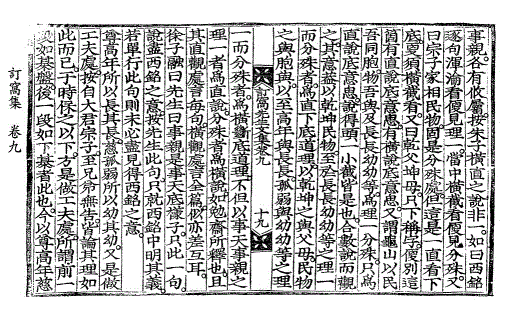 事亲。各有攸属。按朱子横直之说非一。如曰西铭逐句浑沦看便见理一。当中横截看便见分殊。又曰宗子家相民物。固是分殊处。但这是一直看下底。更须横截看。又曰乾父坤母。只下称字。便别这个有直说底意思。有横说底意思。又谓龟山以民吾同胞。物吾与及长长幼幼等。为理一分殊。只为直说底意思。说得头一小截皆是也。合数说而观之。其意盖以乾坤民物。至于长长幼幼等之理一而分殊者。为直下底道理。以乾坤之与父母。民物之与胞与。以至高年与长长。孤弱与幼幼等之理一而分殊者。为横断底道理。不但以事天事亲之理一者为直说。分殊者为横说。如勉斋所释也。且其直观处言每句。横观处言全篇。似亦差互耳。
事亲。各有攸属。按朱子横直之说非一。如曰西铭逐句浑沦看便见理一。当中横截看便见分殊。又曰宗子家相民物。固是分殊处。但这是一直看下底。更须横截看。又曰乾父坤母。只下称字。便别这个有直说底意思。有横说底意思。又谓龟山以民吾同胞。物吾与及长长幼幼等。为理一分殊。只为直说底意思。说得头一小截皆是也。合数说而观之。其意盖以乾坤民物。至于长长幼幼等之理一而分殊者。为直下底道理。以乾坤之与父母。民物之与胞与。以至高年与长长。孤弱与幼幼等之理一而分殊者。为横断底道理。不但以事天事亲之理一者为直说。分殊者为横说。如勉斋所释也。且其直观处言每句。横观处言全篇。似亦差互耳。徐子融曰先生曰事亲是事天底样子。只此一句。说尽西铭之意。按先生此句。只就西铭中明其义。若单行此句则未必尽见得西铭之意。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处。按自大君宗子。至兄弟无告。皆论其理如此而已。于时保之以下。方是做工夫处。所谓前一段如棋盘。后一段如下棋者此也。今以尊高年慈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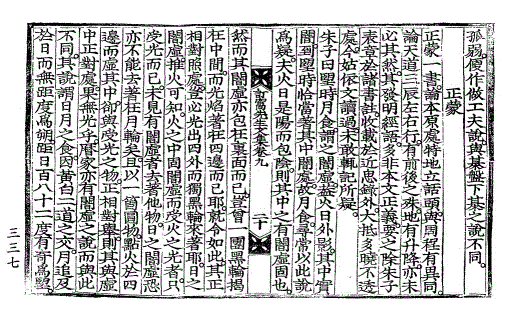 孤弱。便作做工夫说。与棋盘下棋之说不同。
孤弱。便作做工夫说。与棋盘下棋之说不同。正蒙
正蒙一书。论本原处特地立话头。与周程有异同。论天道三辰左右行。有前后之殊。地有升降。亦未必其然。其发明经语。多非本文正义。要之除朱子表章于诸书注。收载于近思录外。大抵多晓不透处。今姑依文读过。未敢辄记所疑。
朱子曰望时月食。谓之闇虚。盖火日外影。其中实闇。到望时恰当著其中闇处。故月食。寻常以此说为疑。夫火日是阳而包阴。则其中之有闇虚固也。然而其闇虚亦包在里面而已。岂曾一团黑轮揭在中间。而光焰著在四边而已耶。就令如此。其正相对照处。岂必光出四外而独黑轮来著耶。日之闇虚。推火可知。火之中固闇虚而受火之光者。只受光而已。未见有闇虚者去著他物。日之闇虚恐亦不能去著在月轮矣。且以一个圆物。点火于四边而虚其中。却与受光之物。正相对举。则其与虚中正对处。果无光乎。历家亦有闇虚之说而与此不同。其说谓日月之食。因黄白二道之交。月追及于日而无距度为朔。距日百八十二度有奇为望。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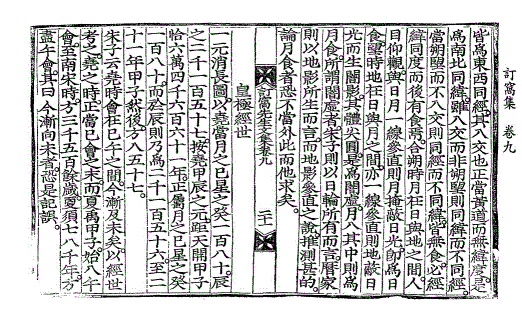 皆为东西同经。其入交也正当黄道而无纬度。是为南北同纬。虽入交而非朔望则同纬而不同经。当朔望而不入交则同经而不同纬。皆无食。必经纬同度而后有食焉。合朔时月在日与地之间。人目仰观。与日月一线参直则月掩蔽日光。即为日食。望时地在日与月之间。亦一线参直则地蔽日光而生闇影。其体尖圆。是为闇虚。月入其中则为月食。所谓闇虚者。朱子则以日轮所有而言。历家则以地影所生而言。而地影参直之说。推测甚的。论月食者恐不当外此而他求矣。
皆为东西同经。其入交也正当黄道而无纬度。是为南北同纬。虽入交而非朔望则同纬而不同经。当朔望而不入交则同经而不同纬。皆无食。必经纬同度而后有食焉。合朔时月在日与地之间。人目仰观。与日月一线参直则月掩蔽日光。即为日食。望时地在日与月之间。亦一线参直则地蔽日光而生闇影。其体尖圆。是为闇虚。月入其中则为月食。所谓闇虚者。朱子则以日轮所有而言。历家则以地影所生而言。而地影参直之说。推测甚的。论月食者恐不当外此而他求矣。皇极经世
一元消长图。以尧当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按尧甲辰之元。距天开甲子恰六万四千六百六十一年。正属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而于辰则乃为二千一百五十六。至二十一年甲子然后。方入五十七。
朱子云尧时会在巳午之间。今渐及未矣。以经世考之。尧之时。正当巳会之末。而夏禹甲子。始入午会。至南宋时。方三千五百馀岁。更须七八千年。方尽午会。其曰今渐向未者。恐是记误。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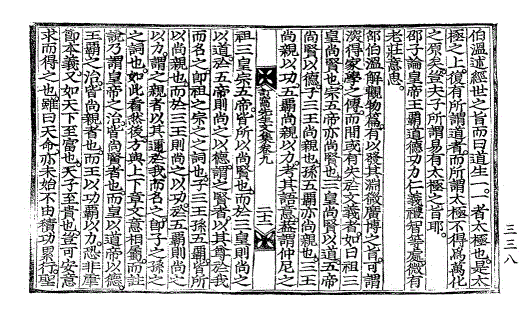 伯温述经世之旨而曰道生一。一者太极也。是太极之上。复有所谓道者。而所谓太极不得为万化之原矣。岂夫子所谓易有太极之旨耶。
伯温述经世之旨而曰道生一。一者太极也。是太极之上。复有所谓道者。而所谓太极不得为万化之原矣。岂夫子所谓易有太极之旨耶。邵子论皇帝王霸道德功力仁义礼智等处。微有老庄意思。
邵伯温解观物篇。有以发其渊微广博之旨。可谓深得家学之传。而间或有失于文义者。如曰祖三皇尚贤也。宗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德。子三王尚亲也。孙五霸亦尚亲也。三王尚亲以功。五霸尚亲以力。考其语意。盖谓仲尼之祖三皇宗五帝。皆所以尚贤也。而于三皇则尚之以道。于五帝则尚之以德。谓之贤者。以其尊于我而名之。即祖之宗之之词也。子三王孙五霸。皆所以尚亲也。而于三王则尚之以功。于五霸则尚之以力。谓之亲者以其迩于我而名之。即子之孙之之词也。如此看然后。方与上下章文意相属。而注说乃谓皇帝之治。皆尚贤者也。而皇以道帝以德。王霸之治。皆尚亲者也。而王以功霸以力。恐非康节本义。又如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贵也。岂可安意求而得之也。虽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圣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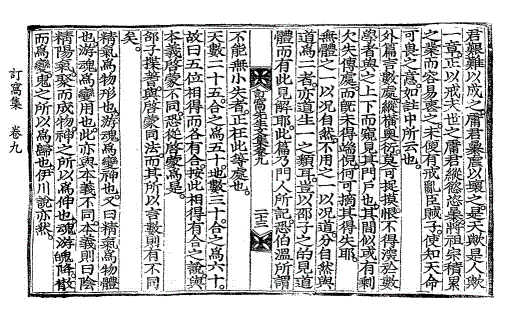 君艰难以成之。庸君㬥虐以坏之。是天欤是人欤一章。正以戒夫世之庸君纵欲恣㬥。将祖宗积累之业而容易丧之。未便有戒乱臣贼子。使知天命可畏之意。如注中所云也。
君艰难以成之。庸君㬥虐以坏之。是天欤是人欤一章。正以戒夫世之庸君纵欲恣㬥。将祖宗积累之业而容易丧之。未便有戒乱臣贼子。使知天命可畏之意。如注中所云也。外篇言数处。纵横奥衍。莫可捉摸。恨不得深于数学者与之上下而窥见其门户也。其间似或有剩欠失传处。而既未得端倪。何可摘其得失耶。
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不用之一以况道。分自然与道为二者。亦道生一之类耳。岂以邵子之的见道体而有此见解耶。此篇乃门人所记。恐伯温所谓不能无小失者。正在此等处也。
天数二十五。合之为五十。地数三十。合之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按此相得有合之说。与本义启蒙不同。恐从启蒙为是。
邵子揲蓍。与启蒙同法。而其所以言数则有不同矣。
精气为物形也。游魂为变神也。又曰精气为物体也。游魂为变用也。此亦与本义不同。本义则曰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所以为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所以为归也。伊川说亦然。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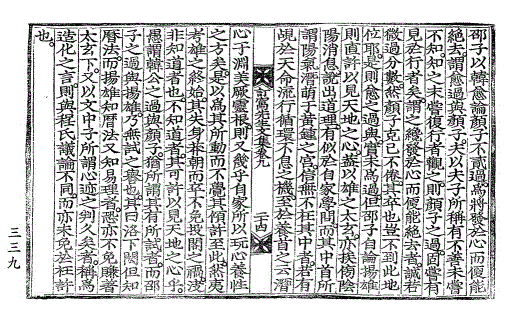 邵子以韩愈论颜子不贰过。为将发于心而便能绝去。谓愈过与颜子。夫以夫子所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者观之。则颜子之过。固尝有见于行者矣。谓之才发于心而便能绝去者。诚若微过分数。然颜子克己不倦。其卒也岂不到此地位耶。是则愈之过与。实未为过。但邵子自论扬雄则直许以见天地之心。盖以雄之太玄。亦挨傍阴阳消息。说出道理。有似于自家学问。而其中首所谓阳气潜萌于黄钟之宫。信无不在其中者。若有觇于天命流行循环不息之机。至于养首之云潜心于渊美厥灵根。则又几乎自家所以玩心养性之方矣。是以为其所动而不觉其倾许至此。然夷考雄之终始。其失身莽朝而卒不免投阁之祸。决非知道者也。不知道者。其可许以见天地之心乎。愚谓韩公之过与颜子。犹所谓其有所试者。而邵子之过与扬雄。乃无试之誉也。其曰洛下闳但知历法。而扬雄知历法又知易理者。恐亦不免赚著太玄下。又以文中子所谓心迹之判久矣者。称为造化之言。则与程氏议论不同。而亦未免于枉许也。
邵子以韩愈论颜子不贰过。为将发于心而便能绝去。谓愈过与颜子。夫以夫子所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者观之。则颜子之过。固尝有见于行者矣。谓之才发于心而便能绝去者。诚若微过分数。然颜子克己不倦。其卒也岂不到此地位耶。是则愈之过与。实未为过。但邵子自论扬雄则直许以见天地之心。盖以雄之太玄。亦挨傍阴阳消息。说出道理。有似于自家学问。而其中首所谓阳气潜萌于黄钟之宫。信无不在其中者。若有觇于天命流行循环不息之机。至于养首之云潜心于渊美厥灵根。则又几乎自家所以玩心养性之方矣。是以为其所动而不觉其倾许至此。然夷考雄之终始。其失身莽朝而卒不免投阁之祸。决非知道者也。不知道者。其可许以见天地之心乎。愚谓韩公之过与颜子。犹所谓其有所试者。而邵子之过与扬雄。乃无试之誉也。其曰洛下闳但知历法。而扬雄知历法又知易理者。恐亦不免赚著太玄下。又以文中子所谓心迹之判久矣者。称为造化之言。则与程氏议论不同。而亦未免于枉许也。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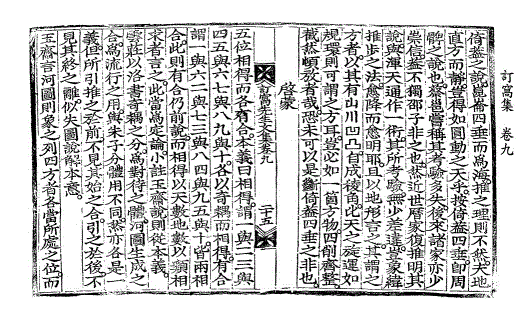 倚盖之说。昆崙四垂而为海。推之理则不然。夫地直方而静。岂得如圆动之天乎。按倚盖四垂。即周髀之说也。蔡邕尝称其考验多失。后来诸家亦少崇信。盖不独邵子非之也。然近世历家复推明其说。与浑天通作一术。其所考验。无少差违。岂象纬推步之法。愈降而愈明耶。且以地形言之。其谓之方者。以其有山川凹凸。自成棱角。比天之旋运如规环则可谓之方耳。岂必如一个方物。四削齐整。截然顿放者哉。恐未可以是断倚盖四垂之非也。
倚盖之说。昆崙四垂而为海。推之理则不然。夫地直方而静。岂得如圆动之天乎。按倚盖四垂。即周髀之说也。蔡邕尝称其考验多失。后来诸家亦少崇信。盖不独邵子非之也。然近世历家复推明其说。与浑天通作一术。其所考验。无少差违。岂象纬推步之法。愈降而愈明耶。且以地形言之。其谓之方者。以其有山川凹凸。自成棱角。比天之旋运如规环则可谓之方耳。岂必如一个方物。四削齐整。截然顿放者哉。恐未可以是断倚盖四垂之非也。启蒙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义曰相得。谓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各以奇耦而相得。有合谓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两相合。此则有合仍前说。而相得以天数地数以类相求者言之。此当为定论。小注玉斋说则从本义。
云庄以洛书奇耦之分。为对待之体。河图生成之合。为流行之用。与朱子分体用不同。然亦各是一义。但所引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似失图说解本意。
玉斋言河图则象之列四方者各当所处之位。而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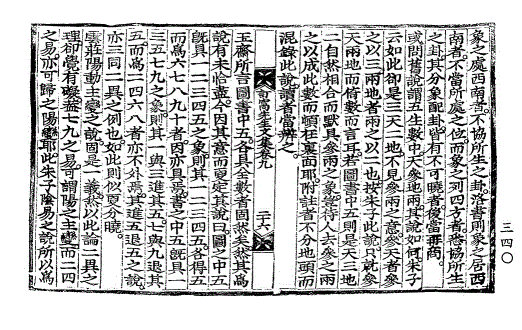 象之处西南者。不协所生之卦。洛书则象之居西南者。不当所处之位。而象之列四方者。悉协所生之卦。其分象配卦。皆有不可晓者。后当再商。
象之处西南者。不协所生之卦。洛书则象之居西南者。不当所处之位。而象之列四方者。悉协所生之卦。其分象配卦。皆有不可晓者。后当再商。或问旧说谓五生数中。天参地两。其说如何。朱子云如此却是三天二地。不见参两之意。参天者参之以三。两地者两之以二也。按朱子此说。只就参天两地而倚数而言耳。若图书中五则是天三地二自然相合而默具参两之象。岂待人去参之两之以成此数而顿在里面耶。附注者不分地头而混录此说。读者当辨之。
玉斋所言图书中五。各具全数者固然矣。然其为说有未恰尽。今因其意而更定其说曰。图之中五既具一二三四五之象。则其一二三四五。各得五而为六七八九十者。因亦具焉。书之中五既具一三五七九之象。则其一与三进其五。七与九退其五。而为二四六八者亦不外焉。其进五退五之说。亦三同二异之例也。如此则似更分晓。
云庄阳动主变之说。固是一义。然以此论二异之理。却觉有碍。盖七九之易。可谓阳之主变。而二四之易。亦可归之阳变耶。此朱子阴易之说所以为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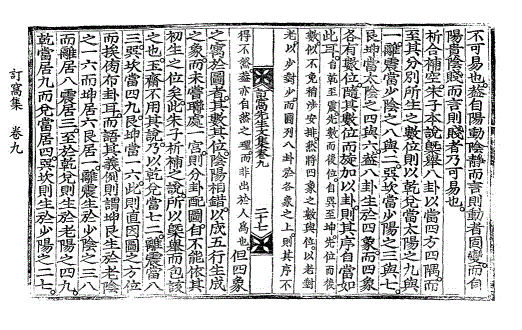 不可易也。盖自阳动阴静而言则动者固变。而自阳贵阴贱而言则贱者乃可易也。
不可易也。盖自阳动阴静而言则动者固变。而自阳贵阴贱而言则贱者乃可易也。析合补空。朱子本说槩举八卦以当四方四隅。而至其分别所生之数位则以乾兑当太阳之九与一。离震当少阴之八与二。巽坎当少阳之三与七。艮坤当太阴之四与六。盖八卦生于四象。而四象各有数位。随其数位而旋加以卦。则其序自当如此耳。(自乾至震。先数而后位。自巽至坤。先位而后数。似不免稍涉安排。然将四象之数与位。以老对老。以少对少。而圆列八卦于各象之上。则其序不得不然。盖亦自然之理。而非出于人为也。)但四象之寓于图者。其数其位。阴阳相错。以成五行生成之象。而未尝联处一宫。则分卦配图。自不能依其初生之位矣。此朱子析补之说。所以槩举而包该之也。玉斋不用其说。乃以乾兑当七二。离震当八三。巽坎当四九。艮坤当一六。此则直因图之方位而挨傍布卦耳。而语其义例则谓坤艮生于老阴之一六而坤居六艮居一。离震生于少阴之三八而离居八震居三。至于乾兑则生于老阳之四九。乾当居九而兑当居四。巽坎则生于少阳之二七。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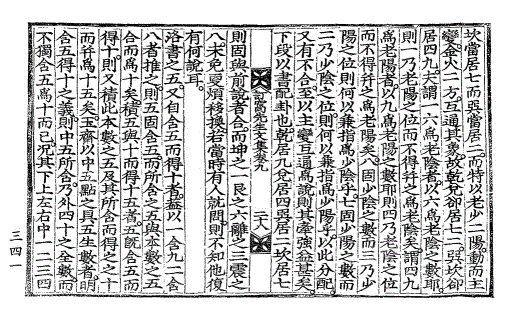 坎当居七而巽当居二。而特以老少二阳。动而主变。金火二方。互通其象。故乾兑却居七二。巽坎却居四九。夫谓一六为老阴者。以六为老阴之数耶。则一乃老阳之位而不得并之为老阴矣。谓四九为老阳者。以九为老阳之数耶则四乃老阴之位而不得并之为老阳矣。八固少阴之数而三乃少阳之位则何以兼指为少阴乎。七固少阳之数而二乃少阴之位。则何以兼指为少阳乎。以此分配。又有不合。至以主变互通为说则其牵强益甚矣。下段以书配卦也。乾居九兑居四巽居二坎居七则固与前说者合。而坤之一艮之六离之三震之八。未免更烦移换。若当时有人就问。则不知他复有何说耳。
坎当居七而巽当居二。而特以老少二阳。动而主变。金火二方。互通其象。故乾兑却居七二。巽坎却居四九。夫谓一六为老阴者。以六为老阴之数耶。则一乃老阳之位而不得并之为老阴矣。谓四九为老阳者。以九为老阳之数耶则四乃老阴之位而不得并之为老阳矣。八固少阴之数而三乃少阳之位则何以兼指为少阴乎。七固少阳之数而二乃少阴之位。则何以兼指为少阳乎。以此分配。又有不合。至以主变互通为说则其牵强益甚矣。下段以书配卦也。乾居九兑居四巽居二坎居七则固与前说者合。而坤之一艮之六离之三震之八。未免更烦移换。若当时有人就问。则不知他复有何说耳。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盖以一含九二含八者推之。则五固含五。而所含之五与本数之五合而为十矣。积五与十而得十五者。五既含五而得十。则又积此本数之五及其所含而得之之十而并为十五矣。玉斋以中五点之具五生数者。明含五得十之义。则中五所含。乃外四十之全数。而不独含五为十而已。况其下上左右中一二三四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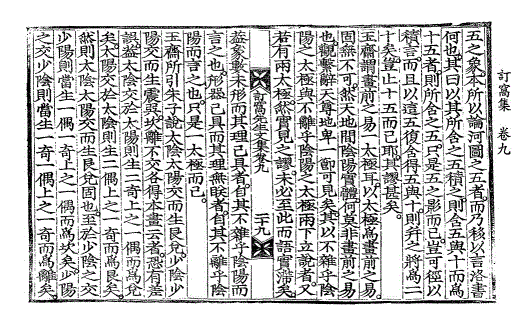 五之象。本所以论河图之五者。而乃移以言洛书何也。其曰以其所含之五积之。则含五与十而为十五者。则所含之五。只是五之影而已。岂可径以积言。而且以这五复含得五与十。则并之将为二十矣。岂止十五而已耶。其谬甚矣。
五之象。本所以论河图之五者。而乃移以言洛书何也。其曰以其所含之五积之。则含五与十而为十五者。则所含之五。只是五之影而已。岂可径以积言。而且以这五复含得五与十。则并之将为二十矣。岂止十五而已耶。其谬甚矣。玉斋谓画前之易一太极耳。以太极为画前之易。固无不可。然天地间阴阳实体。何莫非画前之易也。观系辞天尊地卑一节可见矣。其以不杂乎阴阳之太极与不离乎阴阳之太极两下立说者。又若有两太极。然实见之谬。未必至此而语实滞矣。盖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者。自其不杂乎阴阳而言之也。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者。自其不离乎阴阳而言之也。只是一太极而已。
玉斋所引朱子说太阴太阳交而生艮兑。少阴少阳交而生震巽。坎离不交各得本画云者。恐有差误。盖太阴交于太阳则生二奇上之一偶而为兑矣。太阳交于太阴则生二偶上之一奇而为艮矣。然则太阴太阳交而生艮兑固也。至于少阴之交少阳则当生一偶一奇上之一偶而为坎矣。少阳之交少阴则当生一奇一偶上之一奇而为离矣。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2L 页
 其震巽则少阴之上仍生阴。少阳之上仍生阳。而二卦为各得本画矣。然则生震巽云者。当作生坎离。坎离不交云者。当作震巽不交。而下段所引蕫氏说自两仪生四象则太阳太阴不动而少阴少阳则交。自四象生八卦则乾坤震巽不动而兑离坎艮则交云者。即亦朱子之意也。玉斋不察震巽坎离字之差互。而一向强解。其说安得不纰缪耶。
其震巽则少阴之上仍生阴。少阳之上仍生阳。而二卦为各得本画矣。然则生震巽云者。当作生坎离。坎离不交云者。当作震巽不交。而下段所引蕫氏说自两仪生四象则太阳太阴不动而少阴少阳则交。自四象生八卦则乾坤震巽不动而兑离坎艮则交云者。即亦朱子之意也。玉斋不察震巽坎离字之差互。而一向强解。其说安得不纰缪耶。邵伯温云伊川在康节时。于先天之学。非不问不语之也。按非字可疑。伊川尝曰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馀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一字未尝及数。然则伊川于先天之学。盖未尝问也。何以曰非不问也。设有问焉。岂有伊川问而康节不语乎。愚意非字直为衍文。
玉斋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说。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气。以复当子之后半。一周圆图。而至坤接子之前半。分至四立各当两卦。馀十六节各当三卦。今又因玉斋之说而求其一齐均停。则须以爻分之方。均布于二十四气。乃以十六爻当一气。为图如左。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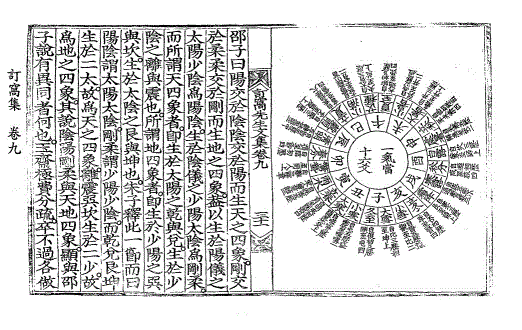 삽화 새창열기
삽화 새창열기邵子曰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盖以生于阳仪之太阳少阴为阳阴。生于阴仪之少阳太阴为刚柔。而所谓天四象者。即生于太阳之乾与兑。生于少阴之离与震也。所谓地四象者。即生于少阳之巽与坎。生于太阴之艮与坤也。朱子释此一节而曰阳阴谓太阳太阴。刚柔谓少阳少阴。而乾兑艮坤生于二太。故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生于二少。故为地之四象。其说阴阳刚柔与天地四象。显与邵子说有异同者何也。玉斋极费分疏。卒不过各做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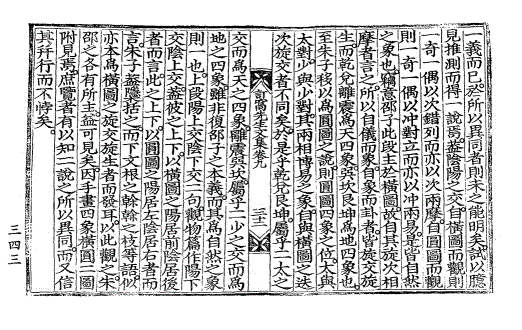 一义而已。于所以异同者则未之能明矣。试以臆见推测而得一说焉。盖阴阳之交。自横图而观则一奇一偶以次错列而亦以次两摩。自圆图而观则一奇一偶以冲对立而亦以冲两易。是皆自然之象也。窃意邵子此段主于横图。故自其旋次相摩者言之。所以自仪而象。自象而卦者。皆旋交旋生。而乾兑离震为天四象。巽坎艮坤为地四象也。至朱子移以为圆图之说。则圆图四象之位。太与太对。少与少对。其两相博易之象。自与横图之迭次旋交者不同矣。于是乎乾兑艮坤。属乎二太之交而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属乎二少之交而为地之四象。虽非复邵子之本义。而其为自然之象则一也。上段阳上交阴下交二句。观物篇作阳下交阴上交。盖彼之上下。以横图之阳居前阴居后者而言。此之上下。以圆图之阳居左阴居右者而言。朱子盖檃括之。而下文根之干干之枝等语。似亦本为横图之旋交旋生者而发耳。以此观之。朱邵之各有所主。益可见矣。因手画四象横圆二图附见焉。庶览者有以知二说之所以异同。而又信其并行而不悖矣。
一义而已。于所以异同者则未之能明矣。试以臆见推测而得一说焉。盖阴阳之交。自横图而观则一奇一偶以次错列而亦以次两摩。自圆图而观则一奇一偶以冲对立而亦以冲两易。是皆自然之象也。窃意邵子此段主于横图。故自其旋次相摩者言之。所以自仪而象。自象而卦者。皆旋交旋生。而乾兑离震为天四象。巽坎艮坤为地四象也。至朱子移以为圆图之说。则圆图四象之位。太与太对。少与少对。其两相博易之象。自与横图之迭次旋交者不同矣。于是乎乾兑艮坤。属乎二太之交而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属乎二少之交而为地之四象。虽非复邵子之本义。而其为自然之象则一也。上段阳上交阴下交二句。观物篇作阳下交阴上交。盖彼之上下。以横图之阳居前阴居后者而言。此之上下。以圆图之阳居左阴居右者而言。朱子盖檃括之。而下文根之干干之枝等语。似亦本为横图之旋交旋生者而发耳。以此观之。朱邵之各有所主。益可见矣。因手画四象横圆二图附见焉。庶览者有以知二说之所以异同。而又信其并行而不悖矣。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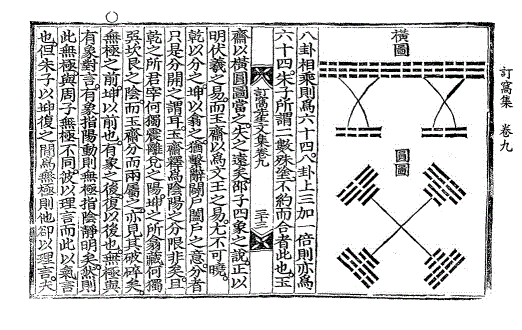 삽화 새창열기
삽화 새창열기八卦相乘则为六十四。八卦上三加一倍则亦为六十四。朱子所谓二数殊涂。不约而合者此也。玉斋以横圆图当之。失之远矣。邵子四象之说。正以明伏羲之易。而玉斋以为文王之易。尤不可晓。
乾以分之。坤以翕之。犹系辞辟户阖户之意。分者只是分开之谓耳。玉斋释为阴阳之分限非矣。且乾之所君宰何独震离兑之阳。坤之所翕藏何独巽坎艮之阴。而玉斋分而两属之。亦见其破碎矣。
无极之前。坤以前也。有象之后。复以后也。无极与有象对言。有象指阳动则无极指阴静明矣。然则此无极。与周子无极不同。彼以理言而此以气言也。但朱子以坤复之间为无极则他却以理言。夫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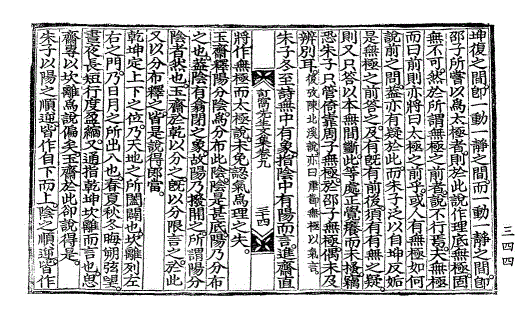 坤复之间。即一动一静之间。而一动一静之间。即邵子所尝以为太极者。则于此说作理底无极。固无不可。然于所谓无极之前者。说不行焉。夫无极而曰前则亦将曰太极之前乎。或人有无极如何说前之问。盖亦有疑于此。而朱子泛以自坤反姤是无极之前答之。及有既有前后。须有有无之疑。则又只答以本无间断。此等处正觉痒而未搔。窃恐朱子只管倚靠周子无极。于邵子无极。偶未及辨别耳。(后考陈北溪说。亦曰康节无极以气言。)
坤复之间。即一动一静之间。而一动一静之间。即邵子所尝以为太极者。则于此说作理底无极。固无不可。然于所谓无极之前者。说不行焉。夫无极而曰前则亦将曰太极之前乎。或人有无极如何说前之问。盖亦有疑于此。而朱子泛以自坤反姤是无极之前答之。及有既有前后。须有有无之疑。则又只答以本无间断。此等处正觉痒而未搔。窃恐朱子只管倚靠周子无极。于邵子无极。偶未及辨别耳。(后考陈北溪说。亦曰康节无极以气言。)朱子冬至诗无中有象。指阴中有阳而言。进斋直将作无极而太极说。未免认气为理之失。
玉斋释阳分阴。为分布此阴。阴是甚底。阳乃分布之也。盖阴有翕闭之象。故阳乃拨开之。所谓阳分阴者然也。玉斋于乾以分之。既以分限言之。于此又以分布释之。皆是说得郎当。
乾坤定上下之位。乃天地之所阖辟也。坎离列左右之门。乃日月之所出入也。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又通指乾坤坎离而言也。思斋专以坎离为说偏矣。玉斋于此却说得是。
朱子以阳之顺逆。皆作自下而上。阴之顺逆。皆作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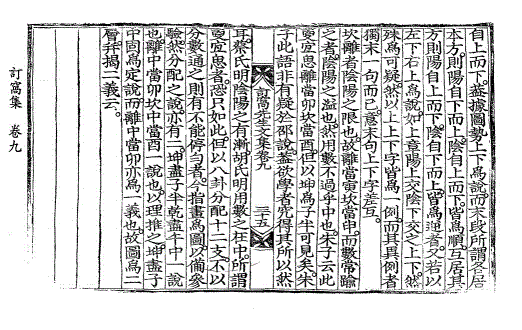 自上而下。盖据图势上下为说。而末段所谓各居本方。则阳自下而上。阴自上而下。皆为顺。互居其方则阳自上而下。阴自下而上。皆为逆者。又若以左下右上为说。如上章阳上交阴下交之上下。然殊为可疑。然以上上下字皆为一例。而其异例者独末一句而已。意末句上下字差互。
自上而下。盖据图势上下为说。而末段所谓各居本方。则阳自下而上。阴自上而下。皆为顺。互居其方则阳自上而下。阴自下而上。皆为逆者。又若以左下右上为说。如上章阳上交阴下交之上下。然殊为可疑。然以上上下字皆为一例。而其异例者独末一句而已。意末句上下字差互。坎离者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踰之者。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中也。朱子云此更宜思离当卯坎当酉。但以坤为子半可见矣。朱子此语非有疑于邵说。盖欲学者究得其所以然耳。蔡氏明阴阳之有渐。胡氏明用数之在中。所谓更宜思者。恐只如此。但以八卦分配十二支。不以分数通之则有不能停匀者。今指画为图。以备参验。然分配之说。亦有二。坤尽子半乾尽午中一说也。离中当卯坎中当酉一说也。以理推之。坤尽子中固为定说。而离中当卯亦为一义也。故图为二层。并揭二义云。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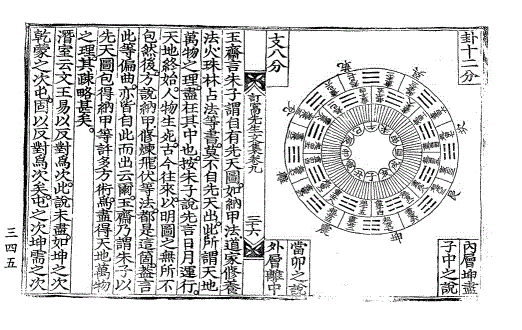 삽화 새창열기
삽화 새창열기玉斋言朱子谓自有先天图。如纳甲法,道家修养法,火珠林占法等书。莫不自先天出。此所谓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也。按朱子说先言日月运行。天地终始。人物生死。古今往来。以明图之无所不包然后。方说纳甲,修炼,飞伏等法。都是这个。盖言此等偏曲。亦皆自此而出云尔。玉斋乃谓朱子以先天图包得纳甲等许多方术。为尽得天地万物之理。其疏略甚矣。
潜室云文王易以反对为次。此说未尽。如坤之次乾蒙之次屯。固以反对为次矣。屯之次坤需之次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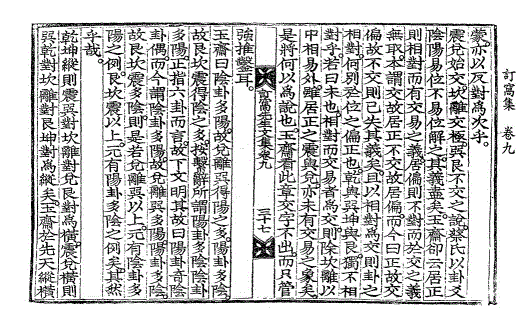 蒙。亦以反对为次乎。
蒙。亦以反对为次乎。震兑始交。坎离交极。巽艮不交之说。蔡氏以卦爻阴阳易位不易位解之。其义尽矣。玉斋却云居正则相对而有交易之义。居偏则不对而于交之义无取。本谓交故居正不交故居偏。而今曰正故交偏故不交则已失其义矣。且以相对为交则卦之相对。何别于位之偏正也。乾与巽坤与艮。独不相对乎。若曰未也。相对而交易者为交。则除坎离以中相易外。虽居正之震与兑。亦未有交易之象矣。是将何以为说也。玉斋看此章交字不出。而只管强推凿耳。
玉斋曰阴卦多阳。故兑离巽得阳之多。阳卦多阴。故艮坎震得阴之多。按系辞所谓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正指六卦而言。故下文明其故曰阳卦奇阴卦偶。而今谓阴卦多阳。故兑离巽多阳。阳卦多阴。故艮坎震多阴。则是若兑离巽以上。元有阴卦多阳之例。艮坎震以上。元有阳卦多阴之例矣。其然乎哉。
乾坤纵则震巽对坎离对兑艮对为横。震兑横则巽乾对坎离对艮坤对为纵矣。玉斋于先天纵横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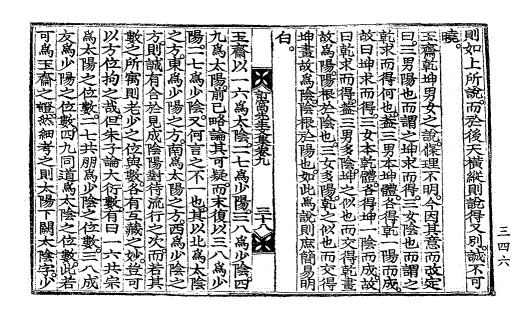 则如上所说。而于后天横纵则说得又别。诚不可晓。
则如上所说。而于后天横纵则说得又别。诚不可晓。玉斋乾坤男女之说。条理不明。今因其意而改定曰。三男阳也而谓之坤求而得。三女阴也而谓之乾求而得何也。盖三男本坤体。各得乾一阳而成。故曰坤求而得。三女本乾体。各得坤一阴而成。故曰乾求而得。盖三男多阴。坤之似也而交得乾画故为阳。阳根于阴也。三女多阳。乾之似也而交得坤画故为阴。阴根于阳也。如此为说则庶简易明白。
玉斋以一六为太阴。二七为少阳。三八为少阴。四九为太阳。前已略论其可疑。而末复以三八为少阳。二七为少阴。又何言之不一也。其以北为太阴之方。东为少阳之方。南为太阳之方。西为少阴之方。则诚有合于见成阴阳对待流行之次。而若其数之所寓则老少之位与数。各有互藏之妙。岂可以方位拘之哉。但朱子论大衍数。有曰一六共宗为太阳之位数。二七共朋为少阴之位数。三八成友为少阳之位数。四九同道为太阴之位数。此若可为玉斋之證。然细考之则太阳下阙太阴字。少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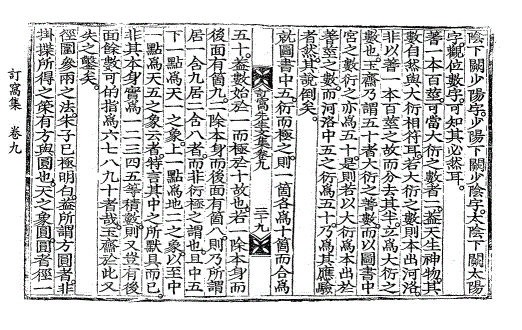 阴下阙少阳字。少阳下阙少阴字。太阴下阙太阳字。观位数字。可知其必然耳。
阴下阙少阳字。少阳下阙少阴字。太阴下阙太阳字。观位数字。可知其必然耳。蓍一本百茎。可当大衍之数者二。盖天生神物。其数自然与大衍相符耳。若大衍之数则本出河洛。非以蓍一本百茎之故而分去其半。立为大衍之数也。玉斋乃谓五十者大衍之蓍数。而以图书中宫之数衍之亦为五十。是则若以大衍为本出于蓍茎之数。而河洛中五之衍为五十。乃为其应验者然。其说倒矣。
就图书中五。衍而极之。则一个各为十个而合为五十。盖数始于一而极于十故也。若一除本身而后面有个九。二除本身而后面有个八。则乃所谓居一含九居二含八者。而非衍极之谓也。且中五下一点为天一之象。上一点为地二之象。以至中一点为天五之象云者。特言其中之所默具而已。非其本身实为一二三四五等积数。则又岂有后面馀数可的指为六七八九十者哉。玉斋于此又失之凿矣。
径围参两之法。朱子已极明白。盖所谓方圆者。非挂揲所得之策有方与圆也。天之象圆。圆者径一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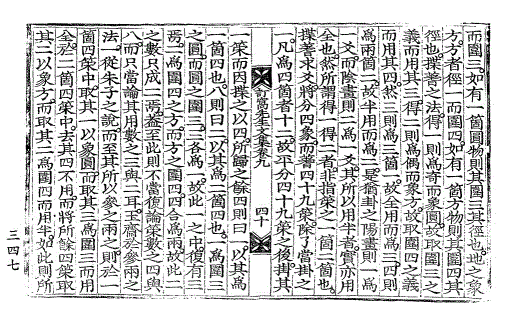 而围三。如有一个圆物则其围三其径也。地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如有一个方物则其围四其径也。揲蓍之法。得一则为奇而象圆。故取围三之义而用其三。得二则为偶而象方。故取围四之义而用其四。然三则为三个一。故全用而为三。四则为两个二。故半用而为二。是犹卦之阳画则一为一爻。而阴画则二为一爻。其所以用半者。实亦用全也。然所谓得一得二者。非指策之一个二个也。揲蓍求爻。将分四象。而蓍四十九策。除了当挂之一。凡为四个者十二。故平分四十九策之后。挂其一策而因揲之以四。所归之馀四则曰一。以其为一个四也。八则曰二。以其为二个四也。一为围三之圆。而圆之围三。三各为一。故此一之中。复有三焉。二为围四之方。而方之围四。四合为两。故此二之数只成二焉。盖至此则不当复论策数之四与八。而只当论其用数之三与二耳。玉斋于参两之法。一从朱子之说。而至其所以参之两之。则于一个四策中。取其一以象圆。而取其三为围三而用全。于二个四策中。去其四不用。而将所馀四策取其二以象方。而取其二为围四而用半。如此则所
而围三。如有一个圆物则其围三其径也。地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如有一个方物则其围四其径也。揲蓍之法。得一则为奇而象圆。故取围三之义而用其三。得二则为偶而象方。故取围四之义而用其四。然三则为三个一。故全用而为三。四则为两个二。故半用而为二。是犹卦之阳画则一为一爻。而阴画则二为一爻。其所以用半者。实亦用全也。然所谓得一得二者。非指策之一个二个也。揲蓍求爻。将分四象。而蓍四十九策。除了当挂之一。凡为四个者十二。故平分四十九策之后。挂其一策而因揲之以四。所归之馀四则曰一。以其为一个四也。八则曰二。以其为二个四也。一为围三之圆。而圆之围三。三各为一。故此一之中。复有三焉。二为围四之方。而方之围四。四合为两。故此二之数只成二焉。盖至此则不当复论策数之四与八。而只当论其用数之三与二耳。玉斋于参两之法。一从朱子之说。而至其所以参之两之。则于一个四策中。取其一以象圆。而取其三为围三而用全。于二个四策中。去其四不用。而将所馀四策取其二以象方。而取其二为围四而用半。如此则所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8H 页
 谓径围者判为两件。三在一外。四在二外。不相包统。而所用之全。不免去一留三而不得为全矣。所用之半。亦半之又半而不成为半矣。是岂朱子图说之意奇偶自然之象哉。于此既失之。而又为图以附于后。极意排布。只成得一场谬法。其得免不知而作之讥耶。
谓径围者判为两件。三在一外。四在二外。不相包统。而所用之全。不免去一留三而不得为全矣。所用之半。亦半之又半而不成为半矣。是岂朱子图说之意奇偶自然之象哉。于此既失之。而又为图以附于后。极意排布。只成得一场谬法。其得免不知而作之讥耶。图说所称旧法。对下文近世之法而言。即朱子本法也。玉斋乃分旧法与今所用为二法。且谓其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及三变之分。得五者三。得四者二。得九者一。得八者二。皆无不同。但其以第一变或五或九皆为奇。后二变或四或八皆为偶者。有不同耳。既又知其初变五九之为奇。再变四八之为偶。姑因其数以目之。而未尝遽以定阴阳之象。则又谓二法虽异。初不害其本同也。此犹称子房事曰此人与留侯少异。然其实则同云尔也。足供一笑。其曰四十九蓍。虚一分二云者。既曰四十九矣。就此虚一而亦有初变五九之数乎。蔡说中四十九蓍虚一分二。将以明阴阳体数之均。故假设而言。玉斋浑称于今旧之法。其亦不察甚矣。
二老皆八。二少皆二十四。以四十九蓍虚一而用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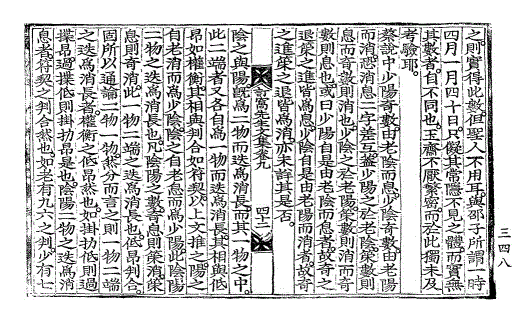 之。则实得此数。但圣人不用耳。与邵子所谓一时四月一月四十日。只儗其常隐不见之体。而实无其数者。自不同也。玉斋不厌繁密。而于此独未及考验耶。
之。则实得此数。但圣人不用耳。与邵子所谓一时四月一月四十日。只儗其常隐不见之体。而实无其数者。自不同也。玉斋不厌繁密。而于此独未及考验耶。蔡说中少阳奇数。由老阴而息。少阴奇数。由老阳而消。恐消息二字差互。盖少阳之于老阴。策数则息而奇数则消也。少阴之于老阳。策数则消而奇数则息也。或曰少阳自是由老阴而息者。故奇之退策之进皆为息。少阴自是由老阳而消者。故奇之进策之退皆为消。亦未详其是否。
阴之与阳。既为二物而迭为消长。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为一物而迭为消长。其相与低昂如权衡。其相与判合如符契。以上文推之。阳之自老消而为少阴。阴之自老息而为少阳。此阴阳二物之迭为消长也。凡阴阳之数。奇息则策消。策息则奇消。此一物二端之迭为消长也。低昂判合。固所以通论二物一物。然分而言之则一物二端之迭为消长者。权衡之低昂然也。如挂扐低则过揲昂。过揲低则挂扐昂是也。阴阳二物之迭为消息者。符契之判合然也。如老有九六之判。少有七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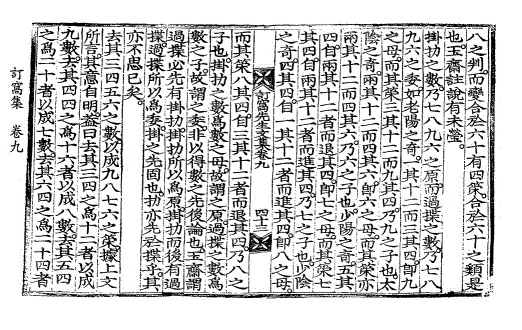 八之判。而变合于六十有四策。合于六十之类是也。玉斋注说有未莹。
八之判。而变合于六十有四策。合于六十之类是也。玉斋注说有未莹。挂扐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原。而过揲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委。如老阳之奇。一其十二而三其四。即九之母。而其策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乃九之子也。太阴之奇。两其十二而四其六。即六之母。而其策亦两其十二而四其六。乃六之子也。少阳之奇。五其四。自两其十二者而退其四。即七之母。而其策七其四。自两其十二者而进其四。乃七之子也。少阴之奇。四其四。自一其十二者而进其四。即八之母。而其策八其四。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其四。乃八之子也。挂扐之数为数之母。故谓之原。过揲之数为数之子。故谓之委。非以得数之先后论也。玉斋谓过揲必先有挂扐。挂扐所以为原。挂扐而后有过揲。过揲所以为委。挂之先固也。扐亦先于揲乎。其亦不思已矣。
去其三四五六之数。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据上文所言。其意自明。盖曰去其三四之为十二者以成九数。去其四四之为十六者以成八数。去其五四之为二十者以成七数。去其六四之为二十四者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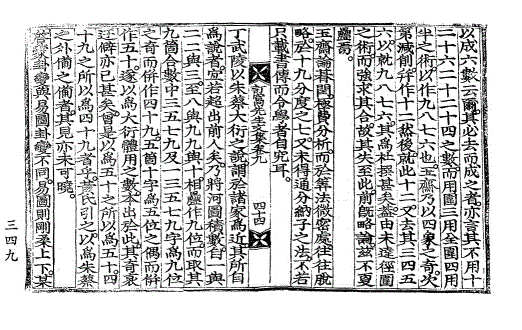 以成六数云尔。其必去而成之者。亦言其不用十二十六二十二十四之数。而用围三用全围四用半之术。以作九八七六也。玉斋乃以四象之奇。次第减削。并作十二然后。就此十二。又去其三四五六。以就九八七六。其为杜撰甚矣。盖由未达径围之术。而强求其合。故其失至此。前既略论。玆不更叠焉。
以成六数云尔。其必去而成之者。亦言其不用十二十六二十二十四之数。而用围三用全围四用半之术。以作九八七六也。玉斋乃以四象之奇。次第减削。并作十二然后。就此十二。又去其三四五六。以就九八七六。其为杜撰甚矣。盖由未达径围之术。而强求其合。故其失至此。前既略论。玆不更叠焉。玉斋论期闰。极费分析。而于算法微密处。往往脱略。于十九分度之七。又未得通分纳子之法。不若只载书传而令学者自究耳。
丁武陵以朱蔡大衍之说。谓于诸家为近。其所自为说者。宜若超出前人矣。乃将河图积数。自一与二二与三。至八与九九与十。相叠作九位。而取其九个合数中三五七九及一三五七九字为九位之奇而并作四十九。五个十字为五位之偶而并作五十。遂以为大衍体用之数。本出于此。其奇哀迂僻亦已甚矣。曾是以为五十之所以为五十。四十九之所以为四十九者乎。黄氏引之。以为朱蔡之外备之备者。其见亦未可晓。
启蒙卦变与易图卦变不同。易图则刚柔上下。某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九 第 3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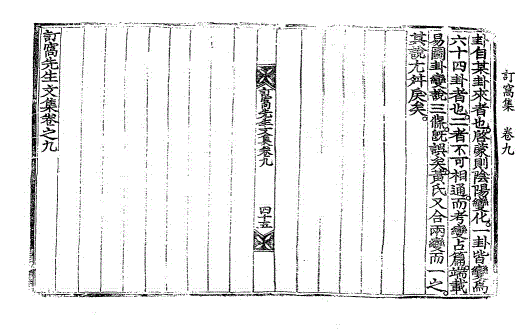 卦自某卦来者也。启蒙则阴阳变化。一卦皆变为六十四卦者也。二者不可相通。而考变占篇。端载易图卦变说三条。既误矣。黄氏又合两变而一之。其说尤舛戾矣。
卦自某卦来者也。启蒙则阴阳变化。一卦皆变为六十四卦者也。二者不可相通。而考变占篇。端载易图卦变说三条。既误矣。黄氏又合两变而一之。其说尤舛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