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书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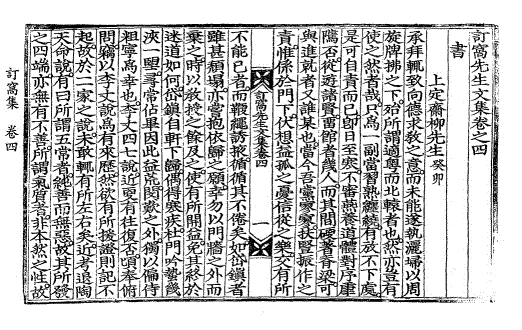 上定斋柳先生(癸卯)
上定斋柳先生(癸卯)承拜辄致向德求教之意。而未能遂执洒埽以周旋牌拂之下。殆所谓适粤而北辕者也。然亦岂有使之然者哉。只为一副当习熟缠绕。有放不下处。是可自责而已。即日至寒。不审燕养道体对序康骘否。从游诸贤。留馆者几人。而其间硬著脊梁。可与进就者又谁某也。当今吾党寥寥。扶竖振作之责。惟系于门下。伏想益孤之忧信从之乐。交有所不能已者。而鞭绳诱掖。循循其不倦矣。如岱镇者虽甚颓塌。亦尝抱依归之愿。幸勿以门墙之外而弃之。时以教授之馀及之。使有所开益。免其终于迷道如何。岱镇自轩下归。偶得寒疾。杜门吟蛰几浃一望。寻常佔毕因此益荒。闵叹之外。独以偏侍粗宁为幸也。李丈四七说。近更有往复否。顷奉俯问。窃以李丈说为有来历。然欲有所援證则记不起。故于二家之说。未敢辄有所左右矣。近考退陶天命说。有曰所谓五常者。纯善而无恶。故其所发之四端。亦无有不善。所谓气质者。非本然之性。故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1L 页
 其所发之七情。易流于邪恶。小山答尹地主问目。亦曰性有本然气质之异。而情有主理主气之分。朱子之言理发气发是也。据此则李丈所言。自是先贤定说。恐不当更费辨论也。如何如何。中庸位育节章句说。以一得之愚。辄蒙俯采。此老先生晚年改物格无极两解之意也。不胜敬服。请更立得小文字。使可以举似人则尤幸也。但于首节章句。有未尽契处。自是迷滞之见。不达于昭旷之地耳。然岱镇于此章。盖尝极费思绎。看得一字一句。俱有下落。是其意见头脑有未易改易者。故敢请门下于此。更审一审。将本文及章句来。平心细意。横竖反覆。使其文字意脉。皆若出于吾之所为然后。徐以一言晓破。则岱镇谨当洗心而遵服焉。所欲质者不一。而烦不敢并溷。当俟进见以请。然蚤晚亦未卜也。惟祝加护静颐。以副瞻仰。
其所发之七情。易流于邪恶。小山答尹地主问目。亦曰性有本然气质之异。而情有主理主气之分。朱子之言理发气发是也。据此则李丈所言。自是先贤定说。恐不当更费辨论也。如何如何。中庸位育节章句说。以一得之愚。辄蒙俯采。此老先生晚年改物格无极两解之意也。不胜敬服。请更立得小文字。使可以举似人则尤幸也。但于首节章句。有未尽契处。自是迷滞之见。不达于昭旷之地耳。然岱镇于此章。盖尝极费思绎。看得一字一句。俱有下落。是其意见头脑有未易改易者。故敢请门下于此。更审一审。将本文及章句来。平心细意。横竖反覆。使其文字意脉。皆若出于吾之所为然后。徐以一言晓破。则岱镇谨当洗心而遵服焉。所欲质者不一。而烦不敢并溷。当俟进见以请。然蚤晚亦未卜也。惟祝加护静颐。以副瞻仰。上定斋柳先生(己酉)
隔岭之地。贻阻门屏。已三岁矣。寻常慊悚。况伏承德门无禄。令子妇青年谢庭。伏惟暮年踽凉之中。慈天燬割。岂比寻常。闻襄事已了。窃计悲扰定而道力胜。保不至损失天和矣。不审服中体候果无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2H 页
 愆度。而牌拂应接。一依平日否。令三从侄秀才以斯文鬯嫡。奄尔夭折。知旧闻聆。已极惊愕。亲懿伤惜。尤如何哉。岱镇数年来。身抱宿痾。绝少轻健之日。惟以废蛰为伎俩。亲年益高。调养失适。每每有愆节。是用有惧而无喜耳。兼值门祚日薄。耆德零谢。龟岘之丧。又系至懿。自此家门典刑。无地考寻。怆痛柰何。兰谷集近营梓役。而事力不敷。极难就绪。且册子虽经佥校。而尚似有未尽整顿处。此间又少勘得此事者。极以闵意也。顷自仲思所蒙示付标数处。觉甚精覈。要当奉依耳。碣铭即七十年未遑之事。而赖宗工属笔。将传信百世。岂惟子孙所感镌。宗族后辈与有幸焉。蒙示草本。窃审文字简重有体裁。德言固如是矣。盛意欲令岱镇商量付标。此古人择荛之意。然蒙陋之见。何以及之。抑盛教故使发难。以为修整之助。则寻常疑禀。或免于不逊之诛耳。略具禀目。别纸呈上。非有所评骘。聊以贡疑而已。
愆度。而牌拂应接。一依平日否。令三从侄秀才以斯文鬯嫡。奄尔夭折。知旧闻聆。已极惊愕。亲懿伤惜。尤如何哉。岱镇数年来。身抱宿痾。绝少轻健之日。惟以废蛰为伎俩。亲年益高。调养失适。每每有愆节。是用有惧而无喜耳。兼值门祚日薄。耆德零谢。龟岘之丧。又系至懿。自此家门典刑。无地考寻。怆痛柰何。兰谷集近营梓役。而事力不敷。极难就绪。且册子虽经佥校。而尚似有未尽整顿处。此间又少勘得此事者。极以闵意也。顷自仲思所蒙示付标数处。觉甚精覈。要当奉依耳。碣铭即七十年未遑之事。而赖宗工属笔。将传信百世。岂惟子孙所感镌。宗族后辈与有幸焉。蒙示草本。窃审文字简重有体裁。德言固如是矣。盛意欲令岱镇商量付标。此古人择荛之意。然蒙陋之见。何以及之。抑盛教故使发难。以为修整之助。则寻常疑禀。或免于不逊之诛耳。略具禀目。别纸呈上。非有所评骘。聊以贡疑而已。上定斋柳先生(乙卯)
瘴海一行。出于五十年静退之馀。正古人所谓会有此者。而抑亦会吾党之不幸矣。严程之日。奔走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2L 页
 劳问。远迩无间。而独岱镇方在浅土哀遑之中。其不敢奔问行李固也。至承临发唁书。而亦未暇控谢矣。然而八耋尊年。千里炎路。扶曳撼顿之节。未尝不入于悬仰也。及陪行人回转。伏闻道涂次舍幸无蹇滞。到配以后。馆接饮膳。不适颐摄。而有以聊遣。气体无损。此诚无入不得之验。固已慰释。而续承六月所出叠唁书。月前又得瓢溪传说。连伏审蒸热以来。旅中道体一向康泰。巾几毕研。日在清燕。此非岂弟令德获劳神明。何以得此。遥不胜攒贺满万。第惟所秉大义。获伸无期。儒疏既被谕退。酉谷疏又承 严谴。此与身分履历夷险可一视者不同。计不能不为之蚤夜忡叹矣。虽然定不定皆天也。亦且柰何哉。顾秉义论事。初非深罪。则当今优老之世。决不令两大耋久于海岛。此则吾党之所拱而俟也。惟是一番声息。动逾时月。而向来平安之报。已属过境。即今节令将再换。更不审旅候起居一如前日。药饵扶摄。书策资玩。仍有以增得一行气力否。南望悬悬。盖不胜倾向也。岱镇襄树既毕。节序累更。拊时哀苦之外。自来不健。加以荒陨。既不能致谨节文。又不能究心书史。颓然
劳问。远迩无间。而独岱镇方在浅土哀遑之中。其不敢奔问行李固也。至承临发唁书。而亦未暇控谢矣。然而八耋尊年。千里炎路。扶曳撼顿之节。未尝不入于悬仰也。及陪行人回转。伏闻道涂次舍幸无蹇滞。到配以后。馆接饮膳。不适颐摄。而有以聊遣。气体无损。此诚无入不得之验。固已慰释。而续承六月所出叠唁书。月前又得瓢溪传说。连伏审蒸热以来。旅中道体一向康泰。巾几毕研。日在清燕。此非岂弟令德获劳神明。何以得此。遥不胜攒贺满万。第惟所秉大义。获伸无期。儒疏既被谕退。酉谷疏又承 严谴。此与身分履历夷险可一视者不同。计不能不为之蚤夜忡叹矣。虽然定不定皆天也。亦且柰何哉。顾秉义论事。初非深罪。则当今优老之世。决不令两大耋久于海岛。此则吾党之所拱而俟也。惟是一番声息。动逾时月。而向来平安之报。已属过境。即今节令将再换。更不审旅候起居一如前日。药饵扶摄。书策资玩。仍有以增得一行气力否。南望悬悬。盖不胜倾向也。岱镇襄树既毕。节序累更。拊时哀苦之外。自来不健。加以荒陨。既不能致谨节文。又不能究心书史。颓然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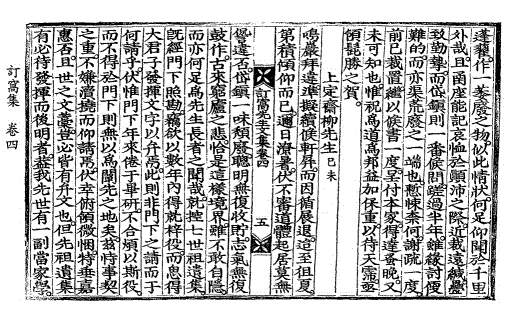 蓬藋。作一萎废之物。似此情状。何足仰闻于千里外哉。且函座能记哀恤于颠沛之际。近裁远缄。叠致勤挚。而岱镇则一番候问。蹉过半年。虽缘讨便难的。而亦渠荒废之一端也。惭悚柰何。谢疏一度。前已裁置。继以候书一度。呈付本家。得达蚤晚。又未可知也。惟祝为道为邦益加保重。以待天霈。亟领髭胜之贺。
蓬藋。作一萎废之物。似此情状。何足仰闻于千里外哉。且函座能记哀恤于颠沛之际。近裁远缄。叠致勤挚。而岱镇则一番候问。蹉过半年。虽缘讨便难的。而亦渠荒废之一端也。惭悚柰何。谢疏一度。前已裁置。继以候书一度。呈付本家。得达蚤晚。又未可知也。惟祝为道为邦益加保重。以待天霈。亟领髭胜之贺。上定斋柳先生(己未)
鸣岩拜违。准拟续候轩屏。而因循展退。迨至徂夏。第积倾仰而已。迩日潦暑。伏不审道体起居莫无愆违否。岱镇一味颓废。聪明无复收贮。志气无复鼓作。古来穷庐之悲。恰是这样境界。虽不敢自隐。而亦何足为先生长者之闻哉。就控七世祖遗集。既经门下照勘。窃欲以数年内得就梓役。而思得大君子发挥文字以弁焉。此则非门下之请而于何请乎。伏惟门下年来倦于毕研。不合烦以斯役。而不得于门下则无以为阐先之地矣。玆恃事契之重。不嫌渎挠而仰请焉。伏幸俯领微悃。特垂嘉惠否。且世之文藁。岂必皆有弁文也。但先祖遗集有必待发挥而后明者。盖我先世有一副当家学。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3L 页
 不务说话而专主行履。自鹤爷虽为溪门的传。而其传授家门者。亦自如此。云川翁有八字诀语。受之家庭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而已。云川临病。申申以此个字面授瓢祖。瓢祖又把做单传之旨。一生服膺之馀。推之为诗礼之传。以今追述。是不过七篇中一段语耳。便似儒士常谈。非比圣门高妙广博之旨。而我先世诸先辈举以为立身第一义。至其所以持守之方。则又决定恁地不恁地而已。未尝费于讲辨而誊于文字。夫穷而所守之义。达而所行之道。固皆有精微之蕴。而非块守两个字所得而尽。则今掉了文字讲说而谓之能持守者。无乃疏乎。然而试考其行履树立。则如芝祖尝处乎穷矣。达则未也。而亦尝历扬于朝矣。在家则乐彝伦安素履。箪瓢晏如。一介无取。至于值岁荐歉。百口艰急。而亲戚宰郡者。了无所闻。在邦则尽忠诚守贞直。审出而恬处。难进而易退。当路致意则厌其热闹而绝不与通。知旧升显则嫌于援附而不复来往。盖其一生所守。真个无慊于道义二字矣。然则其不形于讲辨。不誊于文字者。非不讲而辨也。不誊之以文字也。先祖之世。一时师友盛矣。
不务说话而专主行履。自鹤爷虽为溪门的传。而其传授家门者。亦自如此。云川翁有八字诀语。受之家庭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而已。云川临病。申申以此个字面授瓢祖。瓢祖又把做单传之旨。一生服膺之馀。推之为诗礼之传。以今追述。是不过七篇中一段语耳。便似儒士常谈。非比圣门高妙广博之旨。而我先世诸先辈举以为立身第一义。至其所以持守之方。则又决定恁地不恁地而已。未尝费于讲辨而誊于文字。夫穷而所守之义。达而所行之道。固皆有精微之蕴。而非块守两个字所得而尽。则今掉了文字讲说而谓之能持守者。无乃疏乎。然而试考其行履树立。则如芝祖尝处乎穷矣。达则未也。而亦尝历扬于朝矣。在家则乐彝伦安素履。箪瓢晏如。一介无取。至于值岁荐歉。百口艰急。而亲戚宰郡者。了无所闻。在邦则尽忠诚守贞直。审出而恬处。难进而易退。当路致意则厌其热闹而绝不与通。知旧升显则嫌于援附而不复来往。盖其一生所守。真个无慊于道义二字矣。然则其不形于讲辨。不誊于文字者。非不讲而辨也。不誊之以文字也。先祖之世。一时师友盛矣。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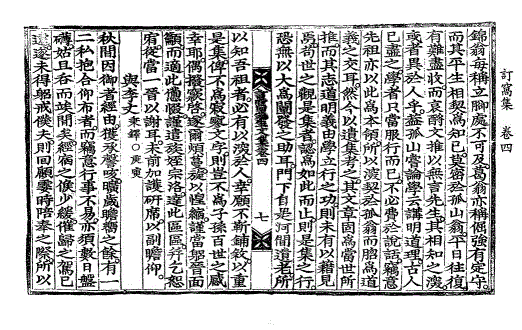 锦翁每称立脚处不可及。葛翁亦称倔强有定守。而其平生相契为知己。莫密于孤山翁。平日往复。有难尽收。而哀酹文推以无言先生。其相知之深。或者异于人乎。盖孤山尝论学云讲明道理。古人已尽之。学者只当服行而已。不必费于说话。窃意先祖亦以此为本领。所以深契于孤翁而吻为道义之交耳。然今以遗集考之。其文章固为当世所推。而其志道明义由学立行之功。则未有以藉见焉。苟世之观是集者。认为如此而止。则是集之行。恐无以大为阐发之助耳。门下自是河间遗老。所以知吾祖者。必有以深于人。幸愿不靳铺叙。以重是集。俾不为寂寥文字。则岂不为子孙百世之感幸耶。偶拨窾启。遂尔烦蔓。旋以惶缩。谨当躬晋面吁。而适此惫惙。谨遣族侄宗洛。达此区区。并乞恕宥。从当一晋以谢耳。未前加护研席。以副瞻仰。
锦翁每称立脚处不可及。葛翁亦称倔强有定守。而其平生相契为知己。莫密于孤山翁。平日往复。有难尽收。而哀酹文推以无言先生。其相知之深。或者异于人乎。盖孤山尝论学云讲明道理。古人已尽之。学者只当服行而已。不必费于说话。窃意先祖亦以此为本领。所以深契于孤翁而吻为道义之交耳。然今以遗集考之。其文章固为当世所推。而其志道明义由学立行之功。则未有以藉见焉。苟世之观是集者。认为如此而止。则是集之行。恐无以大为阐发之助耳。门下自是河间遗老。所以知吾祖者。必有以深于人。幸愿不靳铺叙。以重是集。俾不为寂寥文字。则岂不为子孙百世之感幸耶。偶拨窾启。遂尔烦蔓。旋以惶缩。谨当躬晋面吁。而适此惫惙。谨遣族侄宗洛。达此区区。并乞恕宥。从当一晋以谢耳。未前加护研席。以副瞻仰。与李丈(秉铎○庚寅)
秋间因御者经由。获承謦咳。旷岁瞻向之馀。有一二私抱合仰布者。而窃意行事不易。亦须数日盘礴。姑且吞而俟间矣。经宿之候少缓。催归之驾已远。遂未得躬戒仆夫。则回顾霎时陪奉之际。所以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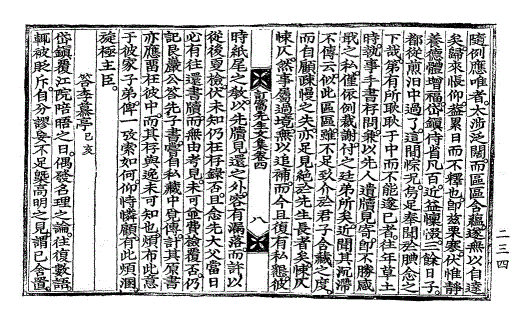 随例应唯者。太涉泛阔。而区区含蕴。遂无以自达矣。归来怅仰。盖累日而不释也。即玆栗寒。伏惟静养德体增福。岱镇侍省凡百。近益懔惙。三馀日子。都从煎汩中过了。这间悰况。乌足奉闻于腆念之下哉。第有所耿耿于中而不能遂已者。往年草土时。执事手书存问。兼以先人遗牍见寄。即不胜感戢之私。仅依例裁谢。付之廷弟所矣。近闻其沉滞不传云。似此区区。虽不足致介于君子含藏之度。而自顾疏慢之失。亦足见绝于先生长者矣。悚仄悚仄。然事属过境。无以追补。而今且复有私恳。彼时纸尾之教。以先牍见还之外。容有漏落。而许以从后更检。伏未知仍在存录否。且念先大父当日必有往还书牍。而无由考见。未可并费检覆否。仍记艮岩公答先子书。尝自私藏中觅传。计其原书亦应留在彼中。而其存与逸未可知也。烦布此意于彼家子弟。俾一考索如何。仰恃怜顾。有此烦溷。旋极主臣。
随例应唯者。太涉泛阔。而区区含蕴。遂无以自达矣。归来怅仰。盖累日而不释也。即玆栗寒。伏惟静养德体增福。岱镇侍省凡百。近益懔惙。三馀日子。都从煎汩中过了。这间悰况。乌足奉闻于腆念之下哉。第有所耿耿于中而不能遂已者。往年草土时。执事手书存问。兼以先人遗牍见寄。即不胜感戢之私。仅依例裁谢。付之廷弟所矣。近闻其沉滞不传云。似此区区。虽不足致介于君子含藏之度。而自顾疏慢之失。亦足见绝于先生长者矣。悚仄悚仄。然事属过境。无以追补。而今且复有私恳。彼时纸尾之教。以先牍见还之外。容有漏落。而许以从后更检。伏未知仍在存录否。且念先大父当日必有往还书牍。而无由考见。未可并费检覆否。仍记艮岩公答先子书。尝自私藏中觅传。计其原书亦应留在彼中。而其存与逸未可知也。烦布此意于彼家子弟。俾一考索如何。仰恃怜顾。有此烦溷。旋极主臣。答李慕亭(己亥)
岱镇覆江院陪晤之日。偶发名理之论。往复数语。辄被贬斥。自分谬妄不足槩高明之见。谓已舍置。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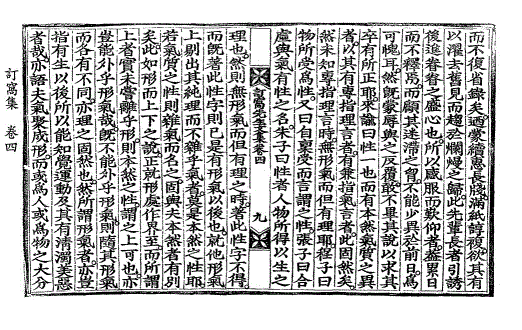 而不复省录矣。乃蒙续惠长笺。满纸谆复。欲其有以濯去旧见而趋于烂熳之归。此先辈长者引诱后进眷眷之盛心也。所以感服而叹仰者。盖累日而不释焉。而顾其迷滞之胸。不能少异于前日。为可愧耳。然既蒙辱与之反覆。敢不毕其说以求其卒有所正耶。来谕曰性一也而有本然气质之异者。以其有专指理言者。有兼指气言者。此固然矣。然未知专指理言时。无形气而但有理耶。程子曰物所受为性。又曰自禀受而言谓之性。张子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朱子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然则无形气而但有理之时。著此性字不得。而既著此性字则已是有形气以后也。就他形气上剔出其纯理而不杂乎气者。莫是本然之性耶。若气质之性则杂气而名之。固与夫本然者有别矣。此如形而上下之说。正就形处作界至。而所谓上者实未尝离乎形。则本然之性。谓之上可也。亦岂能外乎形气哉。既不能外乎形气。则随其形气而各有不同。亦理之固然也。然所谓形气者。亦岂指有生以后所以能知觉运动及其有清浊美恶者哉。亦语夫气聚成形。而或为人或为物之大分
而不复省录矣。乃蒙续惠长笺。满纸谆复。欲其有以濯去旧见而趋于烂熳之归。此先辈长者引诱后进眷眷之盛心也。所以感服而叹仰者。盖累日而不释焉。而顾其迷滞之胸。不能少异于前日。为可愧耳。然既蒙辱与之反覆。敢不毕其说以求其卒有所正耶。来谕曰性一也而有本然气质之异者。以其有专指理言者。有兼指气言者。此固然矣。然未知专指理言时。无形气而但有理耶。程子曰物所受为性。又曰自禀受而言谓之性。张子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朱子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然则无形气而但有理之时。著此性字不得。而既著此性字则已是有形气以后也。就他形气上剔出其纯理而不杂乎气者。莫是本然之性耶。若气质之性则杂气而名之。固与夫本然者有别矣。此如形而上下之说。正就形处作界至。而所谓上者实未尝离乎形。则本然之性。谓之上可也。亦岂能外乎形气哉。既不能外乎形气。则随其形气而各有不同。亦理之固然也。然所谓形气者。亦岂指有生以后所以能知觉运动及其有清浊美恶者哉。亦语夫气聚成形。而或为人或为物之大分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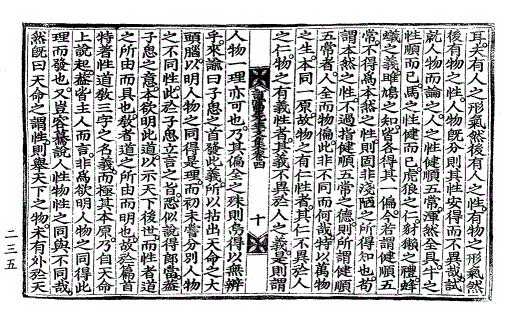 耳。夫有人之形气然后有人之性。有物之形气然后有物之性。人物既分则其性安得而不异哉。试就人物而论之。人之性健顺五常。浑然全具。牛之性顺而已。马之性健而已。虎狼之仁。豺獭之礼。蜂蚁之义。雎鸠之知。皆各得其一偏。今若谓健顺五常。不得为本然之性。则固非浅陋之所得知也。苟谓本然之性。不过指健顺五常之德。则所谓健顺五常者。人全而物偏。此非不同而何哉。特以万物之生。本同一原。故物之有仁性者。其仁不异于人之仁。物之有义性者。其义不异于人之义。是则谓人物一理亦可也。乃其偏全之殊则乌得以无辨乎。来谕曰子思之首发此义。所以拈出天命之大头脑。以明人物之同得是理。而初未尝分别人物之不同性。此于子思立言之旨。恐似说得郎当。盖子思之意。本欲明此道。以示天下后世。而性者道之所由而具也。教者道之所由而明也。故于篇首特著性道教三字之名义。而极其本原。乃自天命上说起。盖皆主人而言。非为欲明人物之同得此理而发也。又岂容蓦说人性物性之同与不同哉。然既曰天命之谓性。则举天下之物。未有外于天
耳。夫有人之形气然后有人之性。有物之形气然后有物之性。人物既分则其性安得而不异哉。试就人物而论之。人之性健顺五常。浑然全具。牛之性顺而已。马之性健而已。虎狼之仁。豺獭之礼。蜂蚁之义。雎鸠之知。皆各得其一偏。今若谓健顺五常。不得为本然之性。则固非浅陋之所得知也。苟谓本然之性。不过指健顺五常之德。则所谓健顺五常者。人全而物偏。此非不同而何哉。特以万物之生。本同一原。故物之有仁性者。其仁不异于人之仁。物之有义性者。其义不异于人之义。是则谓人物一理亦可也。乃其偏全之殊则乌得以无辨乎。来谕曰子思之首发此义。所以拈出天命之大头脑。以明人物之同得是理。而初未尝分别人物之不同性。此于子思立言之旨。恐似说得郎当。盖子思之意。本欲明此道。以示天下后世。而性者道之所由而具也。教者道之所由而明也。故于篇首特著性道教三字之名义。而极其本原。乃自天命上说起。盖皆主人而言。非为欲明人物之同得此理而发也。又岂容蓦说人性物性之同与不同哉。然既曰天命之谓性。则举天下之物。未有外于天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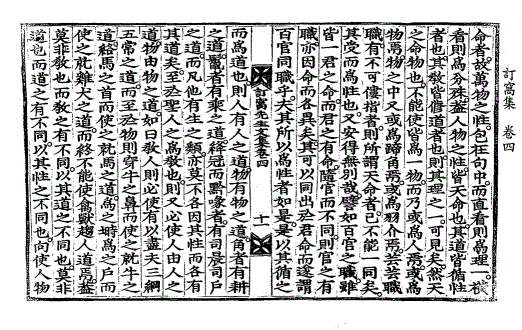 命者。故万物之性。包在句中。而直看则为理一。横看则为分殊。盖人物之性。皆天命也。其道皆循性者也。其教皆修道者也。则其理之一。可见矣。然天之命物也。不能使皆为一物。而乃或为人焉。或为物焉。物之中又或为蹄角焉。或为羽介焉。芸芸职职。有不可偻指者。则所谓天命者。已不能一同矣。其受而为性也。又安得无别哉。譬如百官之职。虽皆一君之命。而君之有命。随官而不同。则官之有职。亦因命而各异矣。其可以同出于君命而遂谓百官同职乎。夫其所以为性者如是。是以其循之而为道也。则人有人之道。物有物之道。角者有耕之道。鬣者有乘之道。绛冠而黔喙者。有司晨司户之道。而凡他有生之类。亦莫不各因其性而各有其道矣。至于圣人之为教也。则又必使人由人之道。物由物之道。如曰教人则必使有以尽夫三纲五常之道。而至于物则穿牛之鼻而使之就牛之道。络马之首而使之就马之道。为之埘为之户而使之就鸡犬之道。而终不能使禽兽趋人道焉。盖莫非教也而教之有不同。以其道之不同也。莫非道也而道之有不同。以其性之不同也。向使人物
命者。故万物之性。包在句中。而直看则为理一。横看则为分殊。盖人物之性。皆天命也。其道皆循性者也。其教皆修道者也。则其理之一。可见矣。然天之命物也。不能使皆为一物。而乃或为人焉。或为物焉。物之中又或为蹄角焉。或为羽介焉。芸芸职职。有不可偻指者。则所谓天命者。已不能一同矣。其受而为性也。又安得无别哉。譬如百官之职。虽皆一君之命。而君之有命。随官而不同。则官之有职。亦因命而各异矣。其可以同出于君命而遂谓百官同职乎。夫其所以为性者如是。是以其循之而为道也。则人有人之道。物有物之道。角者有耕之道。鬣者有乘之道。绛冠而黔喙者。有司晨司户之道。而凡他有生之类。亦莫不各因其性而各有其道矣。至于圣人之为教也。则又必使人由人之道。物由物之道。如曰教人则必使有以尽夫三纲五常之道。而至于物则穿牛之鼻而使之就牛之道。络马之首而使之就马之道。为之埘为之户而使之就鸡犬之道。而终不能使禽兽趋人道焉。盖莫非教也而教之有不同。以其道之不同也。莫非道也而道之有不同。以其性之不同也。向使人物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6L 页
 均同一性。则道也者循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圣人何不以人道率禽兽。使之皆如吾之为贵。而乃独视之为异类。使其同得乎天性之全者。卒不能自免于卑贱之归乎。来谕曰朱子于章句中。只曰人物各得其所赋之理。又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其曰所赋之理。其曰性之自然者。即所谓本然之性也。而其曰各得各循云者。非谓本然之性。物各有异也。此于朱子解经之意。又似看得儱侗。盖其以所赋之理及性之自然者。为本然之性则得矣。而其曰各得各循云者。果无分别人物之意乎。试就章句之说而细解之。其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所以释命也。其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者。所以释性也。其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者。所以释道也。夫自天命之初。必待气以成形而后理有所赋。则其气所成之形。已有人物之分矣。其形所赋之理。独无人物之别乎。故其言得此理而为性则曰各得而为健顺五常之德。其言率此性而为道则曰各循而为日用当行之路。上下各字。
均同一性。则道也者循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圣人何不以人道率禽兽。使之皆如吾之为贵。而乃独视之为异类。使其同得乎天性之全者。卒不能自免于卑贱之归乎。来谕曰朱子于章句中。只曰人物各得其所赋之理。又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其曰所赋之理。其曰性之自然者。即所谓本然之性也。而其曰各得各循云者。非谓本然之性。物各有异也。此于朱子解经之意。又似看得儱侗。盖其以所赋之理及性之自然者。为本然之性则得矣。而其曰各得各循云者。果无分别人物之意乎。试就章句之说而细解之。其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者。所以释命也。其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者。所以释性也。其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者。所以释道也。夫自天命之初。必待气以成形而后理有所赋。则其气所成之形。已有人物之分矣。其形所赋之理。独无人物之别乎。故其言得此理而为性则曰各得而为健顺五常之德。其言率此性而为道则曰各循而为日用当行之路。上下各字。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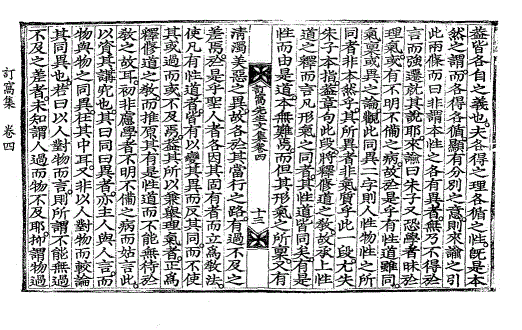 盖皆各自之义也。夫各得之理各循之性。既是本然之谓。而各得各循。显有分别之意。则来谕之引此两条而曰非谓本性之各有异者。无乃不得于言而强迁就其说耶。来谕曰朱子又恐学者昧于理气。或有不明不备之病。故于是乎有性道虽同。气禀或异之论。观此同异二字则人性物性之所同者非本然乎。其所异者非气质乎此一段。尤失朱子本指。盖章句此段。将释修道之教。故承上性道之释而言凡形气之同者。其性道皆同矣。有是性而由是道。本无难焉。而但其形气之所禀。又有清浊美恶之异。故各于其当行之路。有过不及之差焉。于是乎圣人者各因其固有者而立为教法。使凡有性道者。皆有以变其异而反其同。而不使其或过而或不及焉。盖其所以兼举理气者。正为释修道之教。而推原其有是性道而不能无待于教之故耳。初非虑学者不明不备之病而姑言此。以资其讲究也。其曰同曰异者。亦主人与人言。而物与物之同异。在其中耳。又非以人对物而较论其同异也。若曰以人对物而言。则所谓不能无过不及之差者。未知谓人过而物不及耶。抑谓物过
盖皆各自之义也。夫各得之理各循之性。既是本然之谓。而各得各循。显有分别之意。则来谕之引此两条而曰非谓本性之各有异者。无乃不得于言而强迁就其说耶。来谕曰朱子又恐学者昧于理气。或有不明不备之病。故于是乎有性道虽同。气禀或异之论。观此同异二字则人性物性之所同者非本然乎。其所异者非气质乎此一段。尤失朱子本指。盖章句此段。将释修道之教。故承上性道之释而言凡形气之同者。其性道皆同矣。有是性而由是道。本无难焉。而但其形气之所禀。又有清浊美恶之异。故各于其当行之路。有过不及之差焉。于是乎圣人者各因其固有者而立为教法。使凡有性道者。皆有以变其异而反其同。而不使其或过而或不及焉。盖其所以兼举理气者。正为释修道之教。而推原其有是性道而不能无待于教之故耳。初非虑学者不明不备之病而姑言此。以资其讲究也。其曰同曰异者。亦主人与人言。而物与物之同异。在其中耳。又非以人对物而较论其同异也。若曰以人对物而言。则所谓不能无过不及之差者。未知谓人过而物不及耶。抑谓物过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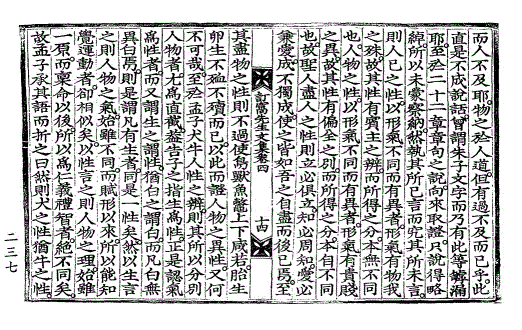 而人不及耶。物之于人道。但有过不及而已乎。此直是不成说话。曾谓朱子文字而乃有此等罅漏耶。至于二十二章章句之说。向来取證。只说得略绰。所以未蒙察纳。然执其所已言而究其所未言。则人己之性。以形气不同而有异者。形气有物我之殊。故其性有宾主之辨。而所得之分。本无不同也。人物之性。以形气不同而有异者。形气有贵贱之异。故其性有偏全之别。而所得之分。本自不同也。故圣人尽人之性则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使之皆如吾之自尽而后已焉。至其尽物之性则不过使鸟兽鱼鳖上下咸若。胎生卵生不殈不殰而已。以此而證人物之异性。又何不可哉。至于孟子犬牛人性之辨。则其所以分别人物者。尤为直截。盖告子之指生为性。正是认气为性者。而又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而凡白无异白焉。则是谓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以生言之则人物之气。始虽不同。而赋形以来。所以能知觉运动者。却相似矣。以性言之则人物之理。始虽一原。而禀命以后。所以为仁义礼智者。绝不同矣。故孟子承其语而折之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
而人不及耶。物之于人道。但有过不及而已乎。此直是不成说话。曾谓朱子文字而乃有此等罅漏耶。至于二十二章章句之说。向来取證。只说得略绰。所以未蒙察纳。然执其所已言而究其所未言。则人己之性。以形气不同而有异者。形气有物我之殊。故其性有宾主之辨。而所得之分。本无不同也。人物之性。以形气不同而有异者。形气有贵贱之异。故其性有偏全之别。而所得之分。本自不同也。故圣人尽人之性则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使之皆如吾之自尽而后已焉。至其尽物之性则不过使鸟兽鱼鳖上下咸若。胎生卵生不殈不殰而已。以此而證人物之异性。又何不可哉。至于孟子犬牛人性之辨。则其所以分别人物者。尤为直截。盖告子之指生为性。正是认气为性者。而又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而凡白无异白焉。则是谓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以生言之则人物之气。始虽不同。而赋形以来。所以能知觉运动者。却相似矣。以性言之则人物之理。始虽一原。而禀命以后。所以为仁义礼智者。绝不同矣。故孟子承其语而折之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8H 页
 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盖曰如子所言则犬牛与人。其生既同。其性亦无异乎云也。而告子之辩遂穷矣。来谕以此性字。看作气质之性。而反语以诘之曰此果为本然之性耶。岱镇则果以为本然之性也。若从来谕作气质看。则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固孟子告子之所同以为同者也。孟子于此。何乃反作不同底物事。而诘告子之以为同也。且告子之意。方谓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皆无不同。而孟子之答。乃曰如此则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亦无不同乎云者。果成答问曲折乎。朱子以此章之说。为微发气质之端者。盖以生同性异之说。比之他章之单言性善。犹为分别理气故耳。初岂以此性字属之气质耶。若果以此性字属之气质。则集注何以分别生之为气性之为理。而继之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云尔也。或问又详之曰犬牛人之形气既具而有知觉能运动者生也。有生虽同。然形气既异则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异。盖在人则得其全而无有不善。在物则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谓性也。今告子谓生之
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盖曰如子所言则犬牛与人。其生既同。其性亦无异乎云也。而告子之辩遂穷矣。来谕以此性字。看作气质之性。而反语以诘之曰此果为本然之性耶。岱镇则果以为本然之性也。若从来谕作气质看。则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固孟子告子之所同以为同者也。孟子于此。何乃反作不同底物事。而诘告子之以为同也。且告子之意。方谓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皆无不同。而孟子之答。乃曰如此则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亦无不同乎云者。果成答问曲折乎。朱子以此章之说。为微发气质之端者。盖以生同性异之说。比之他章之单言性善。犹为分别理气故耳。初岂以此性字属之气质耶。若果以此性字属之气质。则集注何以分别生之为气性之为理。而继之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云尔也。或问又详之曰犬牛人之形气既具而有知觉能运动者生也。有生虽同。然形气既异则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异。盖在人则得其全而无有不善。在物则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谓性也。今告子谓生之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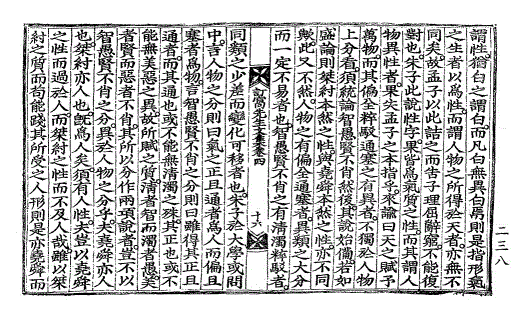 谓性。犹白之谓白。而凡白无异白焉则是指形气之生者以为性。而谓人物之所得于天者。亦无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诘之而告子理屈辞穷。不能复对也。朱子此说性字。果皆为气质之性。而其谓人物异性者。果失孟子之本指乎。来谕曰天之赋予万物。而其偏全粹驳通塞之有异者。不独于人物上分看。须统论智愚贤不肖然后。其说始备。若如盛论则桀纣本然之性。与尧舜本然之性。亦不同欤。此又不然。人物之有偏全通塞者。异类之大分而一定不易者也。智愚贤不肖之有清浊粹驳者。同类之少差而变化可移者也。朱子于大学或问中。言人物之分则曰气之正且通者为人而偏且塞者为物。言智愚贤不肖之分则曰虽得其正且通者。而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殊。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异。故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其所以分作两项说者。岂不以智愚贤不肖之分。异于人物之分乎。夫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既为人矣。须有人性。夫岂以尧舜之性而过于人。而桀纣之性而不及人哉。虽以桀纣之质而苟能践其所受之人形则是亦尧舜而
谓性。犹白之谓白。而凡白无异白焉则是指形气之生者以为性。而谓人物之所得于天者。亦无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诘之而告子理屈辞穷。不能复对也。朱子此说性字。果皆为气质之性。而其谓人物异性者。果失孟子之本指乎。来谕曰天之赋予万物。而其偏全粹驳通塞之有异者。不独于人物上分看。须统论智愚贤不肖然后。其说始备。若如盛论则桀纣本然之性。与尧舜本然之性。亦不同欤。此又不然。人物之有偏全通塞者。异类之大分而一定不易者也。智愚贤不肖之有清浊粹驳者。同类之少差而变化可移者也。朱子于大学或问中。言人物之分则曰气之正且通者为人而偏且塞者为物。言智愚贤不肖之分则曰虽得其正且通者。而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殊。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异。故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其所以分作两项说者。岂不以智愚贤不肖之分。异于人物之分乎。夫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既为人矣。须有人性。夫岂以尧舜之性而过于人。而桀纣之性而不及人哉。虽以桀纣之质而苟能践其所受之人形则是亦尧舜而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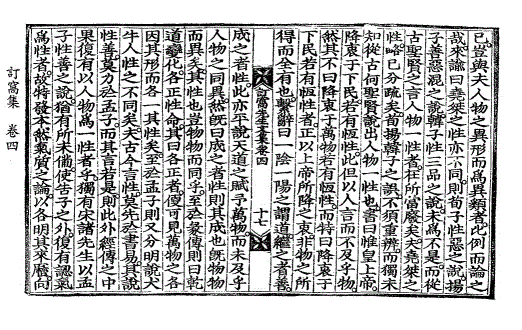 已。岂与夫人物之异形而为异类者。比例而论之哉。来谕曰尧桀之性亦不同。则荀子性恶之说。扬子善恶混之说。韩子性三品之说。未为不是。而从古圣贤之言人物一性者。在所当废矣。夫尧桀之性。略已分疏矣。荀扬韩子之误。不须重辨。而独未知从古何圣贤说出人物一性也。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但以人言而不及乎物。然其不曰降衷于万物若有恒性。而特曰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者。正以上帝所降之衷。非物之所得而全有也。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亦平说天道之赋予万物。而未及乎人物之同异。然既曰成之者性则其成也既物物而异矣。其性也岂物物而同乎。至于彖传则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其曰各正者。便可见万物之各因其形而各一其性矣。至于孟子则又分明说犬牛人性之不同矣。夫古今言性。莫先于书易。其说性善。莫力于孟子。而其言若是。则此外经传之中果复有以人物为一性者乎。独有宋诸先生以孟子性善之说。犹有所未备。使告子之外。复有认气为性者。故特发本然气质之论。以各明其来历。向
已。岂与夫人物之异形而为异类者。比例而论之哉。来谕曰尧桀之性亦不同。则荀子性恶之说。扬子善恶混之说。韩子性三品之说。未为不是。而从古圣贤之言人物一性者。在所当废矣。夫尧桀之性。略已分疏矣。荀扬韩子之误。不须重辨。而独未知从古何圣贤说出人物一性也。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但以人言而不及乎物。然其不曰降衷于万物若有恒性。而特曰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者。正以上帝所降之衷。非物之所得而全有也。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亦平说天道之赋予万物。而未及乎人物之同异。然既曰成之者性则其成也既物物而异矣。其性也岂物物而同乎。至于彖传则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其曰各正者。便可见万物之各因其形而各一其性矣。至于孟子则又分明说犬牛人性之不同矣。夫古今言性。莫先于书易。其说性善。莫力于孟子。而其言若是。则此外经传之中果复有以人物为一性者乎。独有宋诸先生以孟子性善之说。犹有所未备。使告子之外。复有认气为性者。故特发本然气质之论。以各明其来历。向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39L 页
 所谓专指理兼指气者是已。而程夫子性即理三字。遂为千古论性之断案矣。然后又自其所谓性即理者而益推而上之。以极乎万物禀受之前一原大本之理。则以其无名可名而亦谓之性。如张子所谓性者万物之一原。程子所谓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下性字。)朱子所谓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及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者。其说性字。皆指其未有形气时。但有此理者而强名之。就此而言则果可谓人物一性矣。然而人物未生之时。但有个将为性者。而未有个正为性者。其亦名为性者。盖亦推上一层。预名其理。而非正使得性之名义也。乃若子思所言天命之谓性。则其言性字。分明为禀受之名。于此而岂可亦言人物之一同而无所异耶。抑岱镇所以分别人物者。亦非谓无同而但有异也。自性而推其本原则同也。就性而指其当体则异也。是其同异之间。若不争多。而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实系于所异之几希。苟曰同而已则万物之中。吾何以最灵。而传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者。又安在哉。窃恐此说遍行。将使为人者自诿曰禽兽之性。亦如吾性。而
所谓专指理兼指气者是已。而程夫子性即理三字。遂为千古论性之断案矣。然后又自其所谓性即理者而益推而上之。以极乎万物禀受之前一原大本之理。则以其无名可名而亦谓之性。如张子所谓性者万物之一原。程子所谓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下性字。)朱子所谓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及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者。其说性字。皆指其未有形气时。但有此理者而强名之。就此而言则果可谓人物一性矣。然而人物未生之时。但有个将为性者。而未有个正为性者。其亦名为性者。盖亦推上一层。预名其理。而非正使得性之名义也。乃若子思所言天命之谓性。则其言性字。分明为禀受之名。于此而岂可亦言人物之一同而无所异耶。抑岱镇所以分别人物者。亦非谓无同而但有异也。自性而推其本原则同也。就性而指其当体则异也。是其同异之间。若不争多。而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实系于所异之几希。苟曰同而已则万物之中。吾何以最灵。而传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者。又安在哉。窃恐此说遍行。将使为人者自诿曰禽兽之性。亦如吾性。而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0H 页
 彼乃禽乃兽耳。吾虽不得为圣贤。而已免为禽兽。则所以答上天之付畀者。亦已多矣。若是者又将何说以挽之。而亦岂非人物同性之说有以启之耶。至以万物各具之太极。为各有分别。则诚与人物异性之说为一串。吾丈斥之固也。第考来说。始若昼夜逃闪而终有大不可晓处。请复略辨焉。盖岱镇本说。只谓统体则只一本。而各具则有万殊耳。来谕曰若就散殊处。乍见其所具。则有似乎太极之有万亿。而其所具者之所从来底。毕竟是一个浑沦之体散于万物之中。是则似谓各具则有万殊而统体则只一本矣。夫谓统体则只一本而各具则有万殊。与谓各具则有万殊而统体则只一本。语虽相倒而意实无他。何乃执此而攻此也。细审之则乍见云者。熟看则不然也。有似云者。徒似而非真也。是盖以万物之所各具者。为乍看近似底影子。而独以其所从来处一个浑沦之体。为熟看实然底骨子也。诚令如此。朱子何故不独言熟看时实然底同一太极。而乃并说乍看时近似底各一太极也。同一者独为实然而各一者似之而已。则图解何以曰气殊质异。各一其极。无假借
彼乃禽乃兽耳。吾虽不得为圣贤。而已免为禽兽。则所以答上天之付畀者。亦已多矣。若是者又将何说以挽之。而亦岂非人物同性之说有以启之耶。至以万物各具之太极。为各有分别。则诚与人物异性之说为一串。吾丈斥之固也。第考来说。始若昼夜逃闪而终有大不可晓处。请复略辨焉。盖岱镇本说。只谓统体则只一本。而各具则有万殊耳。来谕曰若就散殊处。乍见其所具。则有似乎太极之有万亿。而其所具者之所从来底。毕竟是一个浑沦之体散于万物之中。是则似谓各具则有万殊而统体则只一本矣。夫谓统体则只一本而各具则有万殊。与谓各具则有万殊而统体则只一本。语虽相倒而意实无他。何乃执此而攻此也。细审之则乍见云者。熟看则不然也。有似云者。徒似而非真也。是盖以万物之所各具者。为乍看近似底影子。而独以其所从来处一个浑沦之体。为熟看实然底骨子也。诚令如此。朱子何故不独言熟看时实然底同一太极。而乃并说乍看时近似底各一太极也。同一者独为实然而各一者似之而已。则图解何以曰气殊质异。各一其极。无假借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0L 页
 焉。而后论又何以曰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也。区区浅见。初不敢将太极作浑沦一物有方体底看。而只将作理之实体看了。以为理本一而已。而是理也赋于万物则为万物之性。散于万事则为万事之理。是其散殊之有万者。不容其漫无彼此之分。而各就其中讨其所具。则亦莫非实然之真体也。且如万物之性。固前段之所已辨。而未必信者。至于万事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妇之别兄弟之友朋友之信之类。果亦无粲然之分。而其为各具也。亦岂假借形似而已乎。使于物性事理之外。别有所谓各具之太极。则是固窈窈冥冥而不可知已。若只求之物性事理之间。则其各有分别而各为实体。已可见矣。岂可独指夫所从来底为一个真体。而以其散而各具者。为乍见而近似而已者乎。来谕曰不可道天地间有许多太极。两仪而为两太极。五行而为五太极。万物而为万太极。此物所具之太极。与彼物所具之太极。专不相联属而各自为一物也。岱镇当初亦未尝以这太极立定名数。排作几许个物事。然今就来谕而论之。其于两仪上面已
焉。而后论又何以曰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也。区区浅见。初不敢将太极作浑沦一物有方体底看。而只将作理之实体看了。以为理本一而已。而是理也赋于万物则为万物之性。散于万事则为万事之理。是其散殊之有万者。不容其漫无彼此之分。而各就其中讨其所具。则亦莫非实然之真体也。且如万物之性。固前段之所已辨。而未必信者。至于万事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妇之别兄弟之友朋友之信之类。果亦无粲然之分。而其为各具也。亦岂假借形似而已乎。使于物性事理之外。别有所谓各具之太极。则是固窈窈冥冥而不可知已。若只求之物性事理之间。则其各有分别而各为实体。已可见矣。岂可独指夫所从来底为一个真体。而以其散而各具者。为乍见而近似而已者乎。来谕曰不可道天地间有许多太极。两仪而为两太极。五行而为五太极。万物而为万太极。此物所具之太极。与彼物所具之太极。专不相联属而各自为一物也。岱镇当初亦未尝以这太极立定名数。排作几许个物事。然今就来谕而论之。其于两仪上面已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1H 页
 曰有许多太极则非矣。而至两仪而曰两。五行而曰五。万物而曰万则未为不可。且如阳之健阴之顺。岂不是两个。木行中仁之理。金行中义之理。水火土行中。礼智信之理。岂不是五个。万物各一之性。岂不是万个。而两个五个万个。那个非太极乎。孔子言太极时。未尝分一与万。而至言六爻之道则目之以三极。自三而分而至于万可也。周子言太极时。亦不分一与万。而至言五行之生则名之以五性。自五而散而至于万亦可也。至于朱子则又直言万物之各一太极矣。一物具得一极。而物之数至于万则数其所具而称之以万。何有不可哉。且此物之所具者。不因彼物而得。彼物之所具者。不因此物而足。则其谓互相联属而不得各为一物者。愚不知其何说也。来谕曰自孔子以来。经几千百年。经几千万人。而只云一太极而已。今乃卒然被高明手分中坏了。使此天命全体之冲漠浑全者。片片破碎。零零棼错。无复无极翁本来面目。愚者于此殆口胠而舌不下矣。然以愚观之。孔子未尝于太极上特加一字。而一本万殊。俱包在其中。周子朱子有一太极之云。而其所指而为一
曰有许多太极则非矣。而至两仪而曰两。五行而曰五。万物而曰万则未为不可。且如阳之健阴之顺。岂不是两个。木行中仁之理。金行中义之理。水火土行中。礼智信之理。岂不是五个。万物各一之性。岂不是万个。而两个五个万个。那个非太极乎。孔子言太极时。未尝分一与万。而至言六爻之道则目之以三极。自三而分而至于万可也。周子言太极时。亦不分一与万。而至言五行之生则名之以五性。自五而散而至于万亦可也。至于朱子则又直言万物之各一太极矣。一物具得一极。而物之数至于万则数其所具而称之以万。何有不可哉。且此物之所具者。不因彼物而得。彼物之所具者。不因此物而足。则其谓互相联属而不得各为一物者。愚不知其何说也。来谕曰自孔子以来。经几千百年。经几千万人。而只云一太极而已。今乃卒然被高明手分中坏了。使此天命全体之冲漠浑全者。片片破碎。零零棼错。无复无极翁本来面目。愚者于此殆口胠而舌不下矣。然以愚观之。孔子未尝于太极上特加一字。而一本万殊。俱包在其中。周子朱子有一太极之云。而其所指而为一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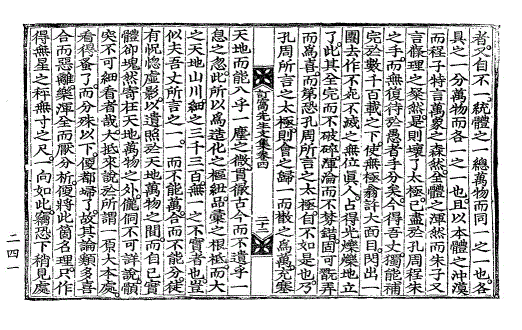 者。又自不一。统体之一总万物而同一之一也。各具之一分万物而各一之一也。且以本体之冲漠而程子特言万象之森然。全体之浑然而朱子又言条理之粲然。是则坏了太极。已尽于孔周程朱之手。而无复待于愚者手分矣。今得吾丈。独能补完于数千百载之下。使无极翁许大面目。闪出一团去作不死不灭之无位真人。占得光烁烁地立了。此其全完而不破碎。浑沦而不棼错。固可玩弄而为喜。而第恐孔周所言之太极。自不如是也。乃孔周所言之太极。则会之归一而散之为万。充塞天地而能入乎一尘之微。贯彻古今而不遗乎一息之忽。此所以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而大之天地山川。细之三千三百。无一之不实者也。岂似夫吾丈所言之一。一而不能万。合而不能分。徒有恍惚虚影。以遗照于天地万物之间。而自己实体却块然寄在天地万物之外。儱侗不可详说。顝突不可细看者哉。大抵来说于所谓一原大本处。看得蚤了。而分殊以下。便都埽了。故其论类多喜合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分析。便将此个名理。只作得无星之秤无寸之尺。一向如此。窃恐下稍见处
者。又自不一。统体之一总万物而同一之一也。各具之一分万物而各一之一也。且以本体之冲漠而程子特言万象之森然。全体之浑然而朱子又言条理之粲然。是则坏了太极。已尽于孔周程朱之手。而无复待于愚者手分矣。今得吾丈。独能补完于数千百载之下。使无极翁许大面目。闪出一团去作不死不灭之无位真人。占得光烁烁地立了。此其全完而不破碎。浑沦而不棼错。固可玩弄而为喜。而第恐孔周所言之太极。自不如是也。乃孔周所言之太极。则会之归一而散之为万。充塞天地而能入乎一尘之微。贯彻古今而不遗乎一息之忽。此所以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而大之天地山川。细之三千三百。无一之不实者也。岂似夫吾丈所言之一。一而不能万。合而不能分。徒有恍惚虚影。以遗照于天地万物之间。而自己实体却块然寄在天地万物之外。儱侗不可详说。顝突不可细看者哉。大抵来说于所谓一原大本处。看得蚤了。而分殊以下。便都埽了。故其论类多喜合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分析。便将此个名理。只作得无星之秤无寸之尺。一向如此。窃恐下稍见处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2H 页
 愈高。而自家受用处愈无交涉。徒有一而无可贯矣。此其为弊。可胜言哉。来谕以岱镇为认气为理。深启末学之弊。然试观前后愚说。果有指气为理处乎。但其所学。未能超出方外。会得道理。不外乎形器。故其言理也。亦未能离气而外求耳。然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如此理会。莫无不可否。仰恃含容之雅。毕陈穿凿之见。而言不知裁。反涉唐突。惟明者之察之也。柳濯叟一番面论。与愚见互有离合。亦不至专然相反。但向后未有文字往复。未知渠所见近更如何。从当以来说转叩耳。不睹不闻说。向来发端而未竟。今亦不暇重溷。然不睹不闻。岱镇亦但谓指思虑未萌。事物未接处言耳。却未知所不睹所不闻云者。指此时心体而言欤。指此时境界而言欤。蚤晚请下一转语以示之也。所示琼章。逐篇珍玩。不胜叹仰。岱镇于此等。盖尝欲学而非其才。故废阁而不复留意久矣。重孤俯索。且以三笑之迹为可贵。露拙续貂。以附童子之笑。计又为之捧腹而绝倒矣。寒威近酷。惟祝加护燕养。以副瞻仰。
愈高。而自家受用处愈无交涉。徒有一而无可贯矣。此其为弊。可胜言哉。来谕以岱镇为认气为理。深启末学之弊。然试观前后愚说。果有指气为理处乎。但其所学。未能超出方外。会得道理。不外乎形器。故其言理也。亦未能离气而外求耳。然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如此理会。莫无不可否。仰恃含容之雅。毕陈穿凿之见。而言不知裁。反涉唐突。惟明者之察之也。柳濯叟一番面论。与愚见互有离合。亦不至专然相反。但向后未有文字往复。未知渠所见近更如何。从当以来说转叩耳。不睹不闻说。向来发端而未竟。今亦不暇重溷。然不睹不闻。岱镇亦但谓指思虑未萌。事物未接处言耳。却未知所不睹所不闻云者。指此时心体而言欤。指此时境界而言欤。蚤晚请下一转语以示之也。所示琼章。逐篇珍玩。不胜叹仰。岱镇于此等。盖尝欲学而非其才。故废阁而不复留意久矣。重孤俯索。且以三笑之迹为可贵。露拙续貂。以附童子之笑。计又为之捧腹而绝倒矣。寒威近酷。惟祝加护燕养。以副瞻仰。答李慕亭(壬寅)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2L 页
 长者有书。不宜稽覆。况承有尚右之戚而久阙慰问之仪。虽蒙雅恕。实深慊悚。即日薰风。伏惟服中体履以时珍护。义理浇灌之乐。定不为外至忧戚所夺矣。岱镇奉老粗遣。但自春后。苦多冗故。此身无閒顿之日。寻常佔毕。一向废阁。时自顾检。方寸太杂。似此悠悠。恐终为君子之弃矣柰何。性命说前书贡愚。不胜支蔓。然非敢谩为浮辩。盖欲罄竭底蕴。以求质于高明之见。而奉读来谕。似只瞥瞥地看过。不曾就肯綮处细意商量。而径立辨论。要以压倒愚言。未说所论得失。只此恐非君子虚中无我之贞也。岱镇虽更有论说。固无以复加于前书。而亦何能使吾丈有所裁察耶。然书中有勿靳更谕之教。且所谓我固未敢自以为是。而子亦安能必其无疑者。尽真切语也。退缩数月。不敢遂已。玆复就来谕中点缀语句。逐段疑禀。不审盛教更以为如何。
长者有书。不宜稽覆。况承有尚右之戚而久阙慰问之仪。虽蒙雅恕。实深慊悚。即日薰风。伏惟服中体履以时珍护。义理浇灌之乐。定不为外至忧戚所夺矣。岱镇奉老粗遣。但自春后。苦多冗故。此身无閒顿之日。寻常佔毕。一向废阁。时自顾检。方寸太杂。似此悠悠。恐终为君子之弃矣柰何。性命说前书贡愚。不胜支蔓。然非敢谩为浮辩。盖欲罄竭底蕴。以求质于高明之见。而奉读来谕。似只瞥瞥地看过。不曾就肯綮处细意商量。而径立辨论。要以压倒愚言。未说所论得失。只此恐非君子虚中无我之贞也。岱镇虽更有论说。固无以复加于前书。而亦何能使吾丈有所裁察耶。然书中有勿靳更谕之教。且所谓我固未敢自以为是。而子亦安能必其无疑者。尽真切语也。退缩数月。不敢遂已。玆复就来谕中点缀语句。逐段疑禀。不审盛教更以为如何。别纸
第一段辨谕曰就他形气上。剔出其纯理而不杂乎气者。是本然之性。若气质之性则固与夫本然者有别。此则与鄙见无异。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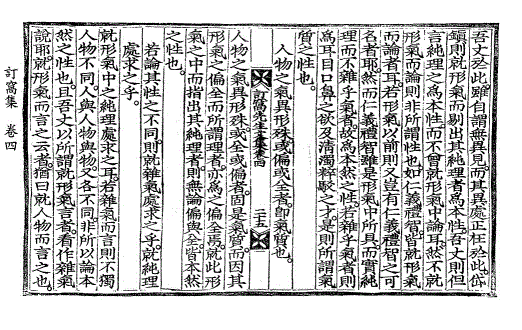 吾丈于此。虽自谓无异见。而其异处正在于此。岱镇则就形气而剔出其纯理者为本性。吾丈则但言纯理之为本性。而不曾就形气中论耳。然不就形气而论则非所谓性也。如仁义礼智。皆就形气而论者耳。若形气以前则又岂有仁义礼智之可名者耶。然而仁义礼智虽是形气中所具。而实纯理而不杂乎气者。故为本然之性。若杂乎气者则为耳目口鼻之欲及清浊粹驳之才。是则所谓气质之性也。
吾丈于此。虽自谓无异见。而其异处正在于此。岱镇则就形气而剔出其纯理者为本性。吾丈则但言纯理之为本性。而不曾就形气中论耳。然不就形气而论则非所谓性也。如仁义礼智。皆就形气而论者耳。若形气以前则又岂有仁义礼智之可名者耶。然而仁义礼智虽是形气中所具。而实纯理而不杂乎气者。故为本然之性。若杂乎气者则为耳目口鼻之欲及清浊粹驳之才。是则所谓气质之性也。人物之气异形殊。或偏或全者。即气质也。
人物之气异形殊。或全或偏者。固是气质。而因其形气之偏全而所谓理者。亦为之偏全焉。就此形气之中而指出其纯理者。则无论偏与全。皆本然之性也。
若论其性之不同。则就杂气处求之乎。就纯理处求之乎。
就形气中之纯理处求之耳。若杂气而言则不独人物不同。人与人物与物。又各不同。非所以论本然之性也。且吾丈以所谓就形气言者。看作杂气说耶。就形气而言之云者。犹曰就人物而言之也。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3L 页
 杂气而言之云者。犹曰以理并气而言之也。吾丈于此恐看不破耳。
杂气而言之云者。犹曰以理并气而言之也。吾丈于此恐看不破耳。人物皆同底大本之性。与人物不同底本然之性。一耶二耶。形气偏全人物不同底性之外。又别有所谓气质之性耶。
人物皆同底大本非性也。前书所谓强名之者耳。此理在人物。为本然之性。而以其在人物。故有偏全之别耳。若气质之性则指此性之杂乎其气者。虽非有两个性。而所言地头。实不同矣。
大本之性为一等。本然之性为一等。气质之性又别为一等。无或近于韩子三品之说耶。
性非有三等。而圣贤论性。实有三层。禀受以前是一层也。禀受以后指其纯理而言者是一层也。指其杂气而言者又一层也。若韩子三品之论则谓仁义礼智之性。有上智中人下愚之别。与三层之说自不同也。
以天之命于物者而为本然之性。
此固然矣。然天之命物。不能独命以理。理本乘气而行。而所乘之气。有许多般样。正底成人。偏底成物。则理之在是者。亦为之偏全焉。所谓气以成形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4H 页
 而理亦赋焉者也。然则天命之性。果无人物之殊乎。且本然之性。固是天命之谓。然其名为本然者。以理之本善而言耳。非谓天之命物之故也。若天之命物则气何尝不与焉耶。独子思所指者。在理而不在气耳。
而理亦赋焉者也。然则天命之性。果无人物之殊乎。且本然之性。固是天命之谓。然其名为本然者。以理之本善而言耳。非谓天之命物之故也。若天之命物则气何尝不与焉耶。独子思所指者。在理而不在气耳。张子所谓形而后有者也。
所谓形而后有者。谓气质之性。因形气而有也。非谓天地之性。已成于有形之前。而此独具于有形之后也。
朱子曰天地之性。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
无论人性物性之全与偏。其理皆太极之本然也。盖所谓偏全者。自人观物之论也。若就物而观物则举著又莫非全体。所谓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者也。就此而言则岂不曰万殊之一本乎。然谓之万殊之一本则非无万殊而但一本也。与吾丈之废万而主一者。恐有间矣。
第二段又恐择焉不精。
所谓有人之形气然后有人之性。有物之形气然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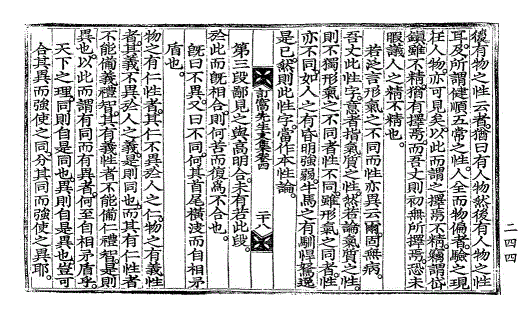 后有物之性云者。犹曰有人物然后有人物之性耳。及所谓健顺五常之性。人全而物偏者。验之现在人物。亦可见矣。以此而谓之择焉不精。窃谓岱镇虽不精。犹有择焉。而吾丈则初无所择焉。恐未暇议人之精不精也。
后有物之性云者。犹曰有人物然后有人物之性耳。及所谓健顺五常之性。人全而物偏者。验之现在人物。亦可见矣。以此而谓之择焉不精。窃谓岱镇虽不精。犹有择焉。而吾丈则初无所择焉。恐未暇议人之精不精也。若泛言形气之不同而性亦异云尔。固无病。
吾丈此性字。意者指气质之性。然若论气质之性。则不独形气之不同者性不同。虽形气之同者。性亦不同。如人之有昏明强弱。牛马之有驯悍驽逸是已。然则此性字。当作本性论。
第三段鄙见之与高明合。未有若此段。
于此而既相合。则何苦而复为不合也。
既曰不异。又曰不同。何其首尾横决而自相矛盾也。
物之有仁性者。其仁不异于人之仁。物之有义性者。其义不异于人之义。是则同也。而其有仁性者不能备义礼智。其有义性者不能备仁礼智。是则异也。以此而谓有同而有异者。何至自相矛盾乎。
天下之理。同则自是同也。异则自是异也。岂可合其异而强使之同。分其同而强使之异耶。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5H 页
 朱子曰同中见其异。异中见其同。不意吾丈之遍考朱训。而独舍此而不讲也。
朱子曰同中见其异。异中见其同。不意吾丈之遍考朱训。而独舍此而不讲也。偏全之义。又与不同尽别。
不同之云。亦有般样。指人与物而曰不同。固不同也。指人之有大小。马之有强弱而曰不同。亦不同也。今见人之论大小强弱而谓之不同者。而曰此大小耳强弱耳。非不同也云尔。则果为成说乎。此等浮辩。恐在所裁省。
犬不可唤做牛之性。牛不可唤做人之性。气质局之也。岂本然之谓哉。
未知犬与牛本具得人之性。而气质局之然后始变移而失了人之性。只做犬与牛耶。不然则人独有本然之性。而犬与牛无本然之性耶。
人为万物之灵而全得健顺五常之德。下此而为物焉则或有一点明处。
此则吾丈所当讳。而亦肯言之何也。岱镇政指五常之具全一路之仅明而谓之不同耳。
顽如木石。微如尘芥者。亦未尝无本然之性。
谓木石尘芥皆有本然之性则得矣。第未知木石尘芥皆具仁义礼智之德。而气质局之然后。始为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5L 页
 顽为微耶。
顽为微耶。譬如水。只是一个水云云。
窃谓性者盛器之水之名也。水虽一也而在器者不能无多寡。理虽一也而在人物者不能无偏全。盖其多寡虽因于器而水实多寡也。偏全虽因于气而理实偏全也。岂可以水之本一而不得复言盛于器者之有多寡。以理之本一而不得复言附于气者之有偏全耶。若器之有污洁而水之有清浊则可比于气质之性。而非所以论本然之性也。
第四段云云。
前谕曰子思之首发此义。所以拈出天命之大头脑。以明人物之同得是理。而初未尝分别人物之不同性。愚意子思立言本意。固非为人物不同性而发也。亦非为人物同性而发也。但举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见其本皆出于天而实不外于我耳。而人物之同异。自包于其中矣。故覆书略言来说之郎当然后。稍以浅见解释本章。以为子思此三句。直看则为理一。横看则为分殊。虽不敢自谓得古圣贤心。而于子思朱子之意。恐不至如来说之几成燕烛矣。且岱镇从初所见。正在于理一分殊。未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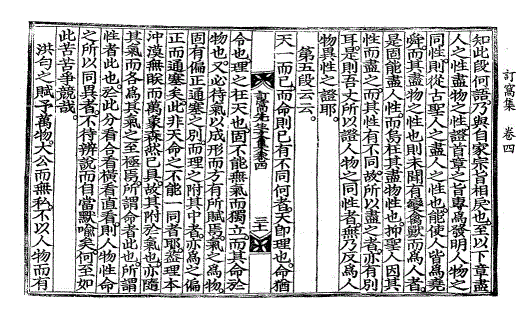 知此段何语。乃与自家宗旨相戾也。至以下章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證首章之旨专为发明人物之同性。则从古圣人之尽人之性也。能使人皆为尧舜。而其尽物之性也则未闻有变禽兽而为人者。是固能尽人性。而乌在其尽物性也。抑圣人因其性而尽之。而其性有不同。故所以尽之者。亦有别耳。是则吾丈所以證人物之同性者。无乃反为人物异性之證耶。
知此段何语。乃与自家宗旨相戾也。至以下章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證首章之旨专为发明人物之同性。则从古圣人之尽人之性也。能使人皆为尧舜。而其尽物之性也则未闻有变禽兽而为人者。是固能尽人性。而乌在其尽物性也。抑圣人因其性而尽之。而其性有不同。故所以尽之者。亦有别耳。是则吾丈所以證人物之同性者。无乃反为人物异性之證耶。第五段云云。
天一而已。而命则已有不同何者。天即理也。命犹令也。理之在天也。固不能无气而独立。而其命于物也。又必待气以成形而方有所赋焉。气之为物。固有偏正通塞之别。而理之附其中者。亦为之偏正而通塞矣。此非天命之不能一同者耶。盖理本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故其附于气也。亦随其气而各为其气之至极焉。所谓命者此也。所谓性者此也。于此分看合看横看直看。则人物性命之所以同异者。不待辨说而自当默喻矣。何至如此苦苦争竞哉。
洪匀之赋予万物。大公而无私。不以人物而有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6L 页
 厚薄。不以贵贱而有爱憎。若曰天命之初。已不能一同。则是似天之赋物。本有爱憎厚薄。
厚薄。不以贵贱而有爱憎。若曰天命之初。已不能一同。则是似天之赋物。本有爱憎厚薄。若谓人物既生然后。上天从而予其性。则其有人物之别。诚不能无厚薄爱憎之嫌。今曰天之命物。不能使皆为一物。则亦来教所谓非天故使之者。就此而言命有不同者。何嫌于以天为不公耶。
或仅通一路。或专然偏塞。而其性之本则无不同。
以吾丈之见。只当曰其性则同。而何以著之本字也。愚亦曰其性之本则同。而其性则不能一同也。
第六段云云。
天之命万物。命在万物始生之初。君之命百官。命在百官已立之后。此吾丈所以差殊看也。然自上世建官之始而观之。则百官之职。固皆由君之命而分为许多事矣。以此而譬万物之受天命而各一性者。岂有不可哉。钦哉亮天工。固所以总命二十二人。而宅百揆作士作司徒汝后稷等许多所命。果无分别乎。
第七段两各字。正如各正性命。各具一太极之各。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7H 页
 愚亦谓两各字。正如各正各具之各。皆各自之义也。
愚亦谓两各字。正如各正各具之各。皆各自之义也。人得此理而为健顺五常。物亦得此理而为健顺五常。虽其偏全之各异。而不害为本然之同也。
只此偏全之异。乃其性之不同也。且吾丈既以人物为同性。则往往著偏全字何也。
人循本然之性而有当行之路。物亦循本然之性而有当行之路。虽其所循之各殊。而亦同出于一本之中矣。
既曰同性。而又曰所循各殊。岂性外别有所循耶。于此请入思议。
第八段云云。
前谕曰朱子恐学者昧于理气。或有不明不备之病。故于是乎有性道虽同。气禀或异之说。观此同异二字。则人性物性之所同者。非本然乎。所异者非气质乎。吾丈之意。分明将性道同气禀异者。作人与物相对说看了。此前后立论张本也。然对人物看则有说不行处。覆书有人过物不及。物过人不及之疑。非敢以胜气加人也。缘文解驳。不得不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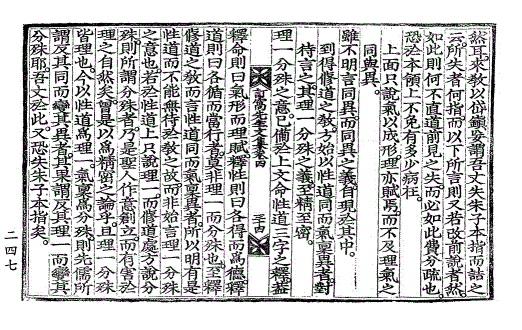 然耳。来教以岱镇妄谓吾丈失朱子本指而诘之云。所失者何指。而以下所言则又若改前说者然。如此则何不直道前见之失。而必如此费分疏也。恐于本领上不免有多少病在。
然耳。来教以岱镇妄谓吾丈失朱子本指而诘之云。所失者何指。而以下所言则又若改前说者然。如此则何不直道前见之失。而必如此费分疏也。恐于本领上不免有多少病在。上面只说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不及理气之同与异。
虽不明言同异。而同异之义。自现于其中。
到得修道之教。方始以性道同而气禀异者。对待言之。其理一分殊之义。至精至密。
理一分殊之意。已备于上文命性道三字之释。盖释命则曰气形而理赋。释性则曰各得而为德。释道则曰各循而当行者。莫非理一而分殊也。至释修道之教而言性道同而气禀异者。所以明有是性道而不能无待于教之故。而非始言理一分殊之意也。若于性道上只说理一。而修道处方说分殊。则所谓分殊者。乃是圣人作意创立。而有害于理之自然矣。曾是以为精密之论乎。且理一分殊皆理也。今以性道为理一。气禀为分殊。则先儒所谓反其同而变其异者。其果谓反其理一而变其分殊耶。吾丈于此。又恐失朱子本指矣。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8H 页
 人物之本性各异则朱子何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也。
人物之本性各异则朱子何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也。在物而为物之性者。亦在人而为人之性者也。故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而为性则实不同。
第九段云云。
孟子所言犬牛人之性。以孟子本语及朱子集注考之。分明为本然之性。而吾丈必欲做气质看。异哉其为辨也。朱夫子微发其端一条。前书略已发明矣。其曰形气不同。故性亦异云者。则所以备孟子之不备。而非指三性为气质之性也。其曰相近者。是指气质之性。如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不同。亦此意云者。则分明与集注及或问不同。必是一时未定之说耳。来教以岱镇未尝遍考朱子说。而遽以己意妆定为说。岱固未能遍考朱训。然其以犬牛人性。为说本然之性。则集注中已有定说。此岂鄙意之所妆定耶。先儒有云朱子说。与章句集注不同者。当以章句集注为正。岱窃以为遍考朱说而疑眩于同异之间。不若谨守集注之为寡过也。至以集注所释。为皆言气质之性。则虽辩博如吾丈。亦恐心眼粗在。今不能更烦焉。请复就生之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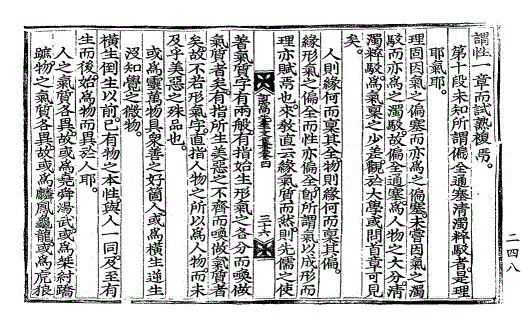 谓性一章而试熟复焉。
谓性一章而试熟复焉。第十段未知所谓偏全通塞清浊粹驳者。是理耶气耶。
理固因气之偏塞而亦为之偏塞。未尝因气之浊驳而亦为之浊驳。故偏全通塞。为人物之大分。清浊粹驳。为气禀之少差。观于大学或问首章可见矣。
人则缘何而禀其全。物则缘何而禀其偏。
缘形气之偏全而性亦偏全。即所谓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也。来教直云缘气质而然。则先儒之使著气质字有两般。有指始生形气之各分而唤做气质者矣。有指所生美恶之不齐而唤做气质者矣。故不若形气字。直指人物之所以为人物。而未及乎美恶之殊品也。
或为灵万物具众善之好个人。或为横生逆生没知觉之微物。
横生倒生以前。已有物之本性。与人一同。及至有生而后。始为物而异于人耶。
人之气质各异。故或为尧舜汤武。或为桀纣蹻蹠。物之气质各异。故或为麟凤龟龙。或为虎狼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9H 页
 蛇蝎。
蛇蝎。尧舜桀纣皆人也。麟凤虎狼非一物也。吾丈比为一例。恐亦不精。
形形色色。有万其性者。非性之本也。
性之本三字。重见于此。未知吾丈以所谓本然之性。唤作性之本耶。然则其命理亦未安。盖本然之性者。只是本善之理也。若曰性之本则天道之自然者是已。
若本然之性则不以人物贤愚而有异。故虽桀蹠之恶而反之则可入于善。虽禽兽之贱而亦有似人之性者。
来教可入于善下。当曰虽禽兽之贱。反之则可至于人。而但曰亦有似人之性者何也。
高明之论。似谓人则得其正且通者而本性既同。则虽有禽兽之行。而固可以同类而曲恕之也。物则得其偏且塞者而本性各异。则虽是同得天地之理者。而绝不与于并生并育之中矣。
区区辨论之意。正欲为人者皆知其本性之贵于禽兽而同于尧舜。无陷于禽兽之行。而必由乎尧舜之道。则自此推之。可以经纶天下。参赞化育。而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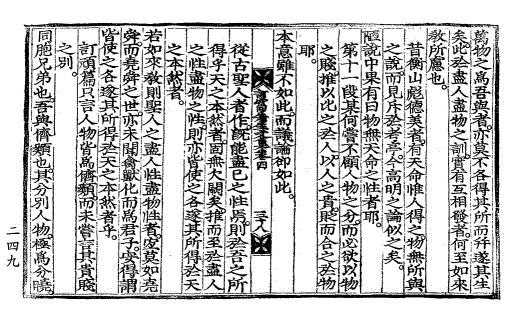 万物之为吾与者。亦莫不各得其所而并遂其生矣。此于尽人尽物之训。实有互相发者。何至如来教所虑也。
万物之为吾与者。亦莫不各得其所而并遂其生矣。此于尽人尽物之训。实有互相发者。何至如来教所虑也。昔衡山彪德美者。有天命惟人得之。物无所与之说。而见斥于考亭。今高明之论似之矣。
陋说中果有曰物无天命之性者耶。
第十一段某何尝不顾人物之分。而必欲以物之贱。推以比之于人。以人之贵。贬而合之于物耶。
本意虽不如此。而议论却如此。
从古圣人者作。既能尽己之性焉。则于吾之所得乎天之本然者。固无欠阙矣。推而至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亦皆使之各遂其所得于天之本然者。
若如来教则圣人之尽人性尽物性者。宜莫如尧舜。而尧舜之世。亦未闻禽兽化而为君子。安得谓皆使之各遂其所得于天之本然者乎。
订顽篇只言人物皆为侪类。而未尝言其贵贱之别。
同胞兄弟也。吾与侪类也。其分别人物。极为分晓。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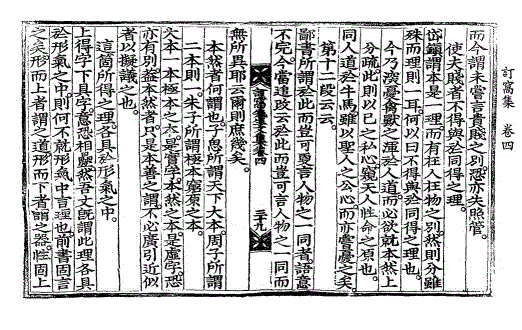 而今谓未尝言贵贱之别。恐亦失照管。
而今谓未尝言贵贱之别。恐亦失照管。使夫贱者不得与于同得之理。
岱镇谓本是一理。而有在人在物之别。然则分虽殊而理则一耳。何以曰不得与于同得之理也。
今乃深忧禽兽之浑于人道。而必欲就本然上分疏。此则以己之私心。窥天人性命之原也。
同人道于牛马。虽以圣人之公心。而亦尝忧之矣。
第十二段云云。
鄙书所谓于此而岂可更言人物之一同者。语意不完。今当追改云于此而岂可言人物之一同而无所异耶云尔则庶几矣。
本然者何谓也。子思所谓天下大本。周子所谓二本则一。朱子所谓极本穷原之本。
大本一本极本之本。是实字。本然之本。是虚字。恐亦有别。盖本然者。只是本善之谓。不必广引近似者以拟议之也。
这个所得之理。各具于形气之中。
上得字下具字。意恐相叠。然吾丈既谓此理各具于形气之中。则何不就形气中言理也。前书固言之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性固上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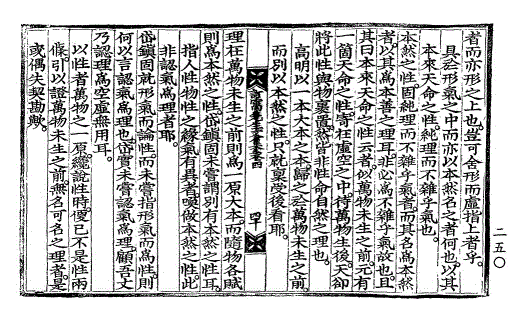 者而亦形之上也。岂可舍形而虚指上者乎。
者而亦形之上也。岂可舍形而虚指上者乎。具于形气之中而亦以本然名之者何也。以其本来天命之性。纯理而不杂乎气也。
本然之性。固纯理而不杂乎气者。而其名为本然者。以其为本善之理耳。非必为不杂乎气故也。且其曰本来天命之性云者。似万物未生之前。元有一个天命之性。寄在虚空之中。待万物生后。天却将此性与物裹置。然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
高明以一本大本之本。归之于万物未生之前。而别以本然之性。只就禀受后看耶。
理在万物未生之前则为一原大本。而随物各赋则为本然之性。岱镇固未尝谓别有本然之性耳。
指人性物性之缘气有异者。唤做本然之性。此非认气为理者耶。
岱镇固就形气而论性。而未尝指形气而为性。则何以言认气为理也。岱实未尝认气为理。顾吾丈乃认理为空虚无用耳。
以性者万物之一原。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两条。引以證万物未生之前。无名可名之理者。是或偶失契勘欤。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1H 页
 性者万物之一原。此性字固可作禀受看。而推上一层作禀受前悬空看则其说尤顺。盖在我之性。已非万物之所原而生者。而惟天地元亨利贞之德。乃万物之所同原也。故岱镇尝以此性字作太极说中天下无性外之物及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之性字看了。至于程子便已不是性云者。犹曰不是性之本云尔。性之本。即禀受以前之理。而直名为性则亦当与图解两性字同看。
性者万物之一原。此性字固可作禀受看。而推上一层作禀受前悬空看则其说尤顺。盖在我之性。已非万物之所原而生者。而惟天地元亨利贞之德。乃万物之所同原也。故岱镇尝以此性字作太极说中天下无性外之物及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之性字看了。至于程子便已不是性云者。犹曰不是性之本云尔。性之本。即禀受以前之理。而直名为性则亦当与图解两性字同看。十三段其曰自性而推其本原则同者是也。而又曰所谓天命者。已不能一同。则其言同者。似同似异。而与张子万物一原之说相背矣。
命固随物而有不同。而其为天命则一也。岂不是万物之一原耶。
或云性同而气异。或云气殊而性亦异。或云气或似而理则异。或云形气虽殊而理则无不同。
朱子尝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其曰性同而气异。曰形气虽殊而理无不同者。自一原而言也。其曰气殊而性亦异。曰气或似而理则异者。自异体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1L 页
 而言也。是皆所以论本然之性。而不及乎气质之性矣。若中庸天命之谓性。则一原异体。皆包于其中。固不可但言其同而不言其异也。此是千古论性断案处。亦乞仔细致思焉。
而言也。是皆所以论本然之性。而不及乎气质之性矣。若中庸天命之谓性。则一原异体。皆包于其中。固不可但言其同而不言其异也。此是千古论性断案处。亦乞仔细致思焉。末段云云。
此段之辨。纵横离合。不可典要。然总而提之。不过谓太极有一而无万耳。夫自统体而观之则太极固一而已。而自其各具者言之。则亦岂无万殊之别乎。吾丈言一本时亦言一。言万殊时亦言一。藉令如此。图解只言万物统体一太极足矣。何更言各具一太极也。吾丈虽亦用万殊字。而实不用万字殊字之意。诚不知其何故耳。见处既如此则何不直云太极者一本而已。其谓有万殊者。皆误云尔也。
通书所谓是万为一一实万分。
如吾丈说则当只曰万为一而已。其曰一实万分者。已剩矣。
细观来说则所谓一本者。固不足以贯乎万焉。而所谓万殊者。亦无与于一矣。
岱镇尝言会之归一而散之为万。即所谓是万为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2H 页
 一一实万分者。来教所云。恐所以自道。而于陋说却使不著也。
一一实万分者。来教所云。恐所以自道。而于陋说却使不著也。非统体之外。别有各具之万太极。而非各具之外。又别有统体之一太极也。
万太极者。未之前见。然孔子以天地人之各一太极而谓之三极。今以万物之各一太极者而谓之万太极。恐亦未为不可。然谓统体之外。别有各具底。各具之外。别有统体底。则诚为丑差。鄙说何段有此般见解也。
易有太极以下。至可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
此段语意粹然无病。不胜叹仰。但未知如此则何以言有一而无万也。
譬如万川之月。光影各殊。而其实则只是一个月也。又如一人之身。分为百子千孙。各得其祖之气脉精神。不可见其气脉之各得而谓之有百千祖也。
此吾丈意见头脑也。天上之月是真体。水中之月是虚影。以此为譬者。正谓一个太极。寄寓在虚空之中。其具于万物者。乃其虚影之遗照。而非其实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2L 页
 体也。是奚可哉。祖考子孙之譬。亦类于此。祖考是一身。子孙又各是一身。理之随物而各具者。果如祖考之别是一身。而徒传其气脉于子孙耶。
体也。是奚可哉。祖考子孙之譬。亦类于此。祖考是一身。子孙又各是一身。理之随物而各具者。果如祖考之别是一身。而徒传其气脉于子孙耶。愚恐统体之一太极。正如禅家所谓无位真人云云。
禅家此话。岱镇尝妄引以况吾丈之见。而吾丈复引之以驳鄙说。未知谓统体各具。俱是实然者。可以当之耶。抑谓统体则实然。而各具则非实然者。可以当之耶。试自反而省焉。若使彼所谓真人。亦无方所无形象。立于万亿佛身之先。而未尝不立于万亿佛身之中。则岱固将引而證太极之各具矣。
程子所谓万象森然。朱子所谓条理粲然云云。
前谕以岱镇说各具之有万殊。为破坏太极而害于全体。故岱引程朱两说。以为统体中。已可以分开说。况就各具处。岂不可分开说云矣。来教却谓误證各具之太极。无乃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耶。所谓坏了太极。已在于圣贤之手者。亦因来谕而云耳。侮圣言之责。恐吾丈宜先自当。而岱分受之而已。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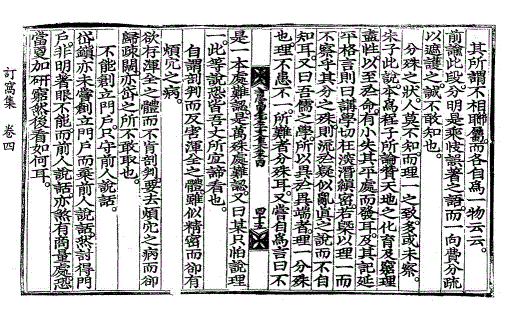 其所谓不相联属。而各自为一物云云。
其所谓不相联属。而各自为一物云云。前谕此段。分明是乘快误著之语。而一向费分疏以遮护之。诚不敢知也。
分殊之状。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
朱子此说。本为程子所论赞天地之化育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有小失其平处而发耳。及其记延平格言则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则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耳。又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又尝自为言曰不是一本处难认。是万殊处难认。又曰某只怕说理一。此等说恐皆吾丈所宜谛看也。
自谓剖判而反害浑全之体。虽似精密而却有烦冗之病。
欲存浑全之体而不肯剖判。要去烦冗之病而却归疏阔。亦岱之所不敢取也。
不能创立门户。只守前人说话。
岱镇亦未尝创立门户而弃前人说话。然讨得门户。非明著眼不能。而前人说话。亦煞有商量处。恐当更加研穷然后看如何耳。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53L 页
 恐是南塘老为祟。
恐是南塘老为祟。南塘说。岱镇盖尝一阅焉。其中固不能无差谬处。而论性一段。却甚精密。恐未可以他说之谬而一齐埽却也。
逐条贡疑。益涉烦冗。兼言不裁择。意近反驳。觉甚惶惧。然雅度善恕。计不至斥绝矣。抑两家之说。反覆看来。其参差离合。只在名言眇忽之际。自此权倚阁往复说话。更就中庸首章三句。益加思索。见得命性道教四字名义地头分分晓晓然后。俟面对讨。以看究竟。似为省事。不审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