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书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1H 页
 上所庵李先生(壬辰)
上所庵李先生(壬辰)岱镇再拜。岱镇向因庐院之会。始遂平昔执鞭之愿。既又仰蒙假以颜色。不斥而外之。而引而进之可教之科。从容讲酬之际。所以开发蒙蔀者郑重焉。自顾无似何以得此。辞退以归。充然若有所得。盖将永以不忘耳。即玆三阳回泰。伏惟君子履端体候增福。居閒玩养之乐。当日以崇深矣。区区不任慰贺之诚。第期制属毕。笃友孔怀。计不以岁月而有杀。其何以裁抑也。岱镇奉老饯迓。又添一惧。兼以懔惙多时。恒事煎汩。似此悰况。有不足仰闻者。寻常翻阅之功。未敢专然放过。然苦未得专一时节。作辍无定。且无明师彊辅以先后之。窃恐前日感发之端。终归于徒然而已。以此益思抽身负笈。趋陪丈席。以做旬月之计而不可得焉。伏恨柰何。其中抱疑而无所质。尤是闵意处。谨具禀目一纸。付溷于将命者。而思之未熟者。姑未敢辄誊颊舌。然其所疑者。亦皆摸捞皮膜。不足以烦崇听。而不知止焉。伏望曲垂恩诲。批而退之。区区之幸也。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1L 页
 馀祝为吾党自爱保重。以慰瞻仰。
馀祝为吾党自爱保重。以慰瞻仰。太极图说问目
图解以太极为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而以阴静为太极之体之立。此两体字。合有分别。窃谓本体之体。就阴阳上推原说本然之妙。即包妙用在其中之体也。体立之体。就太极中分体用说。乃与用相对之体也。然不直以阴静为太极之体。而为体之所以立。则可见其所立之体。只此本体耳。如是分合看如何。
答曰看得是。
第二圈岱镇因此圈妄有见焉。盖此圈左为阳右为阴。而阳中却有阴。阴中却有阳。阴中阳者。静中之动也。阳中阴者。动中之静也。天地间阴阳动静之理。本自如此。故其在人心者亦然。未发之敬。即静中之动也。已发之敬。即动中之静也。盖在天地者。静中无动则无以为动之根。动中无静则无以为静之根。故在人心者。静中无动则灰死木枯而无以为发动之主矣。动中无静则渊沦天飞而无以为定静之用矣。但天地自然而然。人心必有事焉。此则天道人道之别也。如是为说。莫无大悖否。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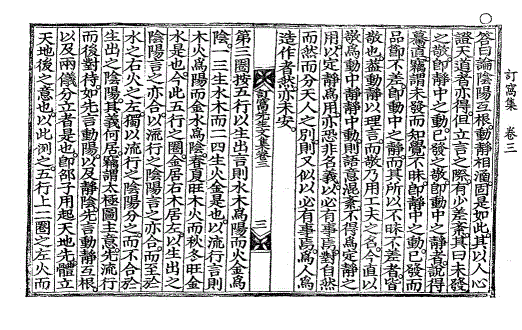 答曰论阴阳互根。动静相涵。固是如此。其以人心證天道者亦得。但立言之际。有少差紊。其曰未发之敬。即静中之动。已发之敬。即动中之静者。说得蓦直。窃谓未发而知觉不昧。即静中之动。已发而品节不差。即动中之静。而其所以不昧不差者。皆敬也。盖动静以理言。而敬乃用工夫之名。今直以敬为动中静静中动。则语意混紊。不得为定静之用。以定静为用。亦恐非名义。以必有事焉。对自然而然而分天人之别。则又似以必有事焉。为人为造作者然。亦未安。
答曰论阴阳互根。动静相涵。固是如此。其以人心證天道者亦得。但立言之际。有少差紊。其曰未发之敬。即静中之动。已发之敬。即动中之静者。说得蓦直。窃谓未发而知觉不昧。即静中之动。已发而品节不差。即动中之静。而其所以不昧不差者。皆敬也。盖动静以理言。而敬乃用工夫之名。今直以敬为动中静静中动。则语意混紊。不得为定静之用。以定静为用。亦恐非名义。以必有事焉。对自然而然而分天人之别。则又似以必有事焉。为人为造作者然。亦未安。第三圈按五行以生出言则水木为阳而火金为阴。一三生水木而二四生火金是也。以流行言则木火为阳而金水为阴。春夏旺木火而秋冬旺金水是也。今此五行之圈。金居右木居左。以生出之阴阳言之亦合。以流行之阴阳言之亦合。而至于水之右火之左。独以流行之阴阳分之。而不合于生出之阴阳。其义何居。窃谓太极图主意。先流行而后对待。如先言动阳。以及静阴。先言动静互根。以及两仪分立者是也。即邵子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之意也。以此例之。五行上二圈之左火而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2L 页
 右水者。主乎流行之阴阳也。下二圈之左木而右金者。主乎对待之阴阳也。此亦先流行后对待之意也。盖此图交系之画。已自具流行对待之象。而其于上下左右。亦有是象焉。盖横看直看。无非这个耳。不审如何。
右水者。主乎流行之阴阳也。下二圈之左木而右金者。主乎对待之阴阳也。此亦先流行后对待之意也。盖此图交系之画。已自具流行对待之象。而其于上下左右。亦有是象焉。盖横看直看。无非这个耳。不审如何。答曰五行排布。朱子以流行言。勉斋以生出言。后来先辈。欲兼二说看。其说甚多。未知适从。而今又生出别话头来。信乎义理之无穷也。盖造化纷纶。条绪极多。说得不患无说。然朱子非不知有生出之序。而断以流行解剥。亦岂无所见哉。今于四圈之内。分其上下。各属生行。證之以图说。质之以邵诗。说得虽似巧密。而一圈之内。要膂断折。上下之间。意象顿绝。恐非造化自然之体如何。
精粗本末无彼此。乃者庐院时。因斋中佥益言。谨闻丈席之教。以精粗本末属之阴阳。以无彼此者为释一太极之意。而以精粗本末。分属太极阴阳者为不然。岱镇固尝抱疑。而反覆考究。终觉后说为得。盖此上句之释五行一阴阳也。既以五殊二实分属而明之矣。则其释阴阳一太极也。独不用分属之例乎。夫或泛就事物上论其一理。则固可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3H 页
 言事物之精粗本末。无彼此皆是理云矣。今以精粗本末。论太极阴阳。则太极岂不是精也本也。阴阳岂不是粗也末也。图说后论及通书解。亦用精粗本末字。后论则就道体浑然中明其有粲然者。如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亦其粲然之一。而统而断之曰精粗本末之分。有不可毫釐差者。通解则正释五殊二实。二本则一而有自末缘本自本之末之语。此皆以太极为精为本。阴阳为粗为末矣。何独以图解之精粗本末字。为不可分属看也。至所谓无彼此云者。犹云此亦彼彼亦此。如明道所谓器亦道道亦器之云也。今以精粗本末。专属阴阳。而以无彼此三字。为一太极之意。则其以精粗本末释阴阳者。已非的确之训。而其以无彼此释一太极者。亦未免无结杀。仅可以得其意于言外也。此岂朱子训释之例乎。
言事物之精粗本末。无彼此皆是理云矣。今以精粗本末。论太极阴阳。则太极岂不是精也本也。阴阳岂不是粗也末也。图说后论及通书解。亦用精粗本末字。后论则就道体浑然中明其有粲然者。如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亦其粲然之一。而统而断之曰精粗本末之分。有不可毫釐差者。通解则正释五殊二实。二本则一而有自末缘本自本之末之语。此皆以太极为精为本。阴阳为粗为末矣。何独以图解之精粗本末字。为不可分属看也。至所谓无彼此云者。犹云此亦彼彼亦此。如明道所谓器亦道道亦器之云也。今以精粗本末。专属阴阳。而以无彼此三字。为一太极之意。则其以精粗本末释阴阳者。已非的确之训。而其以无彼此释一太极者。亦未免无结杀。仅可以得其意于言外也。此岂朱子训释之例乎。答曰熊氏于图体注。以太极为精阴阳为粗。太极为本阴阳为末。而葛庵以为极丑差。盖以太极二五相对。分精粗本末为未安也。庐院时举似此言。而鄙意欲从葛翁。盛论既本熊氏说。则何敢辄加疑难哉。但所引后论精粗本末处。恐看得未审。盖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3L 页
 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云者。是说精粗本末之理。如所谓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者。非以道与器相对说而指谓浑然中之粲然也。通书解适无卷。未及检看。不敢妄说。
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云者。是说精粗本末之理。如所谓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者。非以道与器相对说而指谓浑然中之粲然也。通书解适无卷。未及检看。不敢妄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按五行之生。如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固是阳变阴合而生者也。至于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却似阴变阳合而生者。而总而称之曰阳变阴合而生云云。未知别有其说欤。抑未知不论奇耦而只是生之者为阳变。成之者为阴合耶。不然则此图未及言成之处。而只以水与木为阳变而生。火与金为阴合而生耶。
答曰阳主变阴主合。变合字不可互换用。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则未分奇耦。而生之者为阳变。成之者为阴合。此说是未及言成之处。而只以水木为阳变而生。火金为阴合而生。此说不是。
各一其性。按所谓各一其性者。即解中所谓各具一太极也。盖太极即性。性即太极也。然其立文命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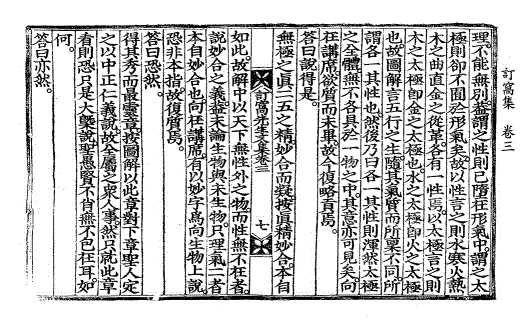 理。不能无别。盖谓之性则已堕在形气中。谓之太极则却不囿于形气矣。故以性言之则水寒火热木之曲直金之从革。各有一性焉。以太极言之则木之太极即金之太极也。水之太极即火之太极也。故图解言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然后乃曰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其意亦可见矣。向在讲席。欲质而未毕。故今复略贡焉。
理。不能无别。盖谓之性则已堕在形气中。谓之太极则却不囿于形气矣。故以性言之则水寒火热木之曲直金之从革。各有一性焉。以太极言之则木之太极即金之太极也。水之太极即火之太极也。故图解言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然后乃曰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其意亦可见矣。向在讲席。欲质而未毕。故今复略贡焉。答曰说得是。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按真精妙合。本自如此。故解中以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说妙合之义。盖未论生物与未生物。只理气二者本自妙合也。向在讲席。有以妙字为向生物上说。恐非本指。故复质焉。
答曰恐然。
得其秀而最灵章。按图解以此章对下章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说。故全属之众人事。然只就此章看则恐只是大槩说。圣愚贤不肖无不包在耳。如何。
答曰亦然。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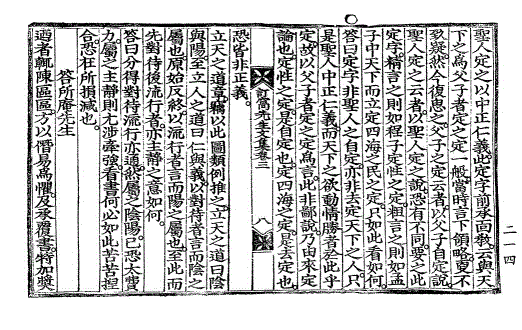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此定字前承面教。云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之定一般。当时言下领略。更不致疑。然今复思之。父子之定云者。以父子自定说。圣人定之云者。以圣人定之说。恐有不同。要之此定字。精言之则如程子定性之定。粗言之则如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定。只如此看如何。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此定字前承面教。云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之定一般。当时言下领略。更不致疑。然今复思之。父子之定云者。以父子自定说。圣人定之云者。以圣人定之说。恐有不同。要之此定字。精言之则如程子定性之定。粗言之则如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定。只如此看如何。答曰定字非圣人之自定。亦非去定天下之人。只是圣人中正仁义。而天下之欲动情胜者于此乎定。故以父子者定之定为言。此非鄙说。乃由来定论也。定性之定。是自定也。定四海之定。是去定也。恐皆非正义。
立天之道章。窃以此图类例推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对待者言而阴之属也。原始反终。以流行者言而阳之属也。至此而先对待后流行者。亦主静之意如何。
答曰分得对待流行亦通。然属之阴阳。已恐太费力。属之主静则尤涉牵强。看书何必如此苦苦捏合。恐在所损减也。
答所庵先生
乃者辄陈区区。方以僭易为惧。及承覆书。特加奖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5H 页
 饬。十行倾倒。意溢言表。自揣愚分。祇有愧感。便后又经一朓朒。伏不审燕养体候一向康福。区区瞻仰。盖无虚日也。岱镇老人近失将摄。遂致感顿。数日调度。极增煎惧。计非一两日可已。顾合下颓塌之质。每堕在忧患窟里。一个身心。无少宁静时。寻常口耳之学。亦且因循放下。深恐遂归于小人之科。无以自见于先生长者矣。疑目批诲。开发谆至。谨已三复而拜赐矣。顾其间犹有所听莹者。自知迷滞之胸。所蔽已厚。其开之固难矣。然而蓄疑不发。亦前辈之所戒也。谨复条列以上。兼以庐院时所质而未决者若干条仰渎焉。伏望明赐覆诲。无使终于迷蔽如何。第伏念日用行为之间。初无真切体验之功。而敢开口作此个说话。有若居常从事者然。真所谓言之无怍者。其得免大方之所斥退耶。愧悚愧悚。签面二字。岱镇非敢信口妄称。盖自庐院以后。深有依归之愿。虽绊身冗汩。未得辄供洒埽之役。而其计则固已定矣。所以因尺书之候。以微见向德之诚。而下教乃退避而不肯受。乃君子撝谦之美则有之矣。得无沮吾党趋向者之望乎。此岱镇所以虽承谴斥而犹不能知止也。幸
饬。十行倾倒。意溢言表。自揣愚分。祇有愧感。便后又经一朓朒。伏不审燕养体候一向康福。区区瞻仰。盖无虚日也。岱镇老人近失将摄。遂致感顿。数日调度。极增煎惧。计非一两日可已。顾合下颓塌之质。每堕在忧患窟里。一个身心。无少宁静时。寻常口耳之学。亦且因循放下。深恐遂归于小人之科。无以自见于先生长者矣。疑目批诲。开发谆至。谨已三复而拜赐矣。顾其间犹有所听莹者。自知迷滞之胸。所蔽已厚。其开之固难矣。然而蓄疑不发。亦前辈之所戒也。谨复条列以上。兼以庐院时所质而未决者若干条仰渎焉。伏望明赐覆诲。无使终于迷蔽如何。第伏念日用行为之间。初无真切体验之功。而敢开口作此个说话。有若居常从事者然。真所谓言之无怍者。其得免大方之所斥退耶。愧悚愧悚。签面二字。岱镇非敢信口妄称。盖自庐院以后。深有依归之愿。虽绊身冗汩。未得辄供洒埽之役。而其计则固已定矣。所以因尺书之候。以微见向德之诚。而下教乃退避而不肯受。乃君子撝谦之美则有之矣。得无沮吾党趋向者之望乎。此岱镇所以虽承谴斥而犹不能知止也。幸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5L 页
 有以俯恕之如何。馀伏祝加护摄养。庸副下忱。
有以俯恕之如何。馀伏祝加护摄养。庸副下忱。问目
动中静静中动疑目中。未发已发之敬云者。诚是说得蓦直。因此而得闻精切之诲。伏幸伏幸。至于定静之用云者。对上发动之主而言。盖曰发动者之主。定静者之用云尔。非便以定静为用也。至以必有事焉。对自然而然。而为天道人道之分则其意犹中庸之以诚为天道。以诚之为人道。而非敢以必有事焉。为人为造作也。凡此皆言语不伶俐。致烦辨诲。益觉赧汗也。
五行圈此条之说。承教以后谨已濯去旧见。然此一圈左右上下位置次序。终有不能释然者。盖以生出言则水当居左而火当居右也。以流行言则木当先火而金当先水也。而今此水火之左右。既不合生出之位置。金木之处下。又不合流行之次序。则此将何所适从也。间尝反覆参验而得其槩焉。盖以左右言之。阴阳圈虽左阳右阴。而居左之阳却包个阴。居右之阴却包个阳。则左固非无阴之方。而右亦非无阳之方矣。水虽生于天一而却为包阳之阴。故坎之为卦。二阴而含一阳。是犹阴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6H 页
 阳圈右方之画也。火虽生于地二而却为包阴之阳。故离之为卦。二阳而含一阴。是犹阴阳圈左方之画也。于此各主其所重而分定其位置。则岂不可以水居右而以火居左乎。若以上下言之。五行之生。自微而著。水火者形气之始也。金木者形气之成也。故水火无成质而金木有定形。是亦当以水火居上金木居下。以从其形气生成之次序也。由是观之。周子之排布是圈。固未尝以生出定左右。亦未尝以流行分上下。而其生出流行之象。别具于圈中交系之画。如自水而火而木而金而土者。乃其生出之次也。其自水而木而火而土而金者。乃其流行之序也。如此看得。稍快心眼。但复与图解阴阳稚盛之说不合。更觉掣碍之为病耳。勉斋说曾闻其小异于图解。而此无性理书。未得考检其说果何如。伏望明赐辨诲。祛此蒙蔽。
阳圈右方之画也。火虽生于地二而却为包阴之阳。故离之为卦。二阳而含一阴。是犹阴阳圈左方之画也。于此各主其所重而分定其位置。则岂不可以水居右而以火居左乎。若以上下言之。五行之生。自微而著。水火者形气之始也。金木者形气之成也。故水火无成质而金木有定形。是亦当以水火居上金木居下。以从其形气生成之次序也。由是观之。周子之排布是圈。固未尝以生出定左右。亦未尝以流行分上下。而其生出流行之象。别具于圈中交系之画。如自水而火而木而金而土者。乃其生出之次也。其自水而木而火而土而金者。乃其流行之序也。如此看得。稍快心眼。但复与图解阴阳稚盛之说不合。更觉掣碍之为病耳。勉斋说曾闻其小异于图解。而此无性理书。未得考检其说果何如。伏望明赐辨诲。祛此蒙蔽。答曰五行阴阳之说。本无定体。横说竖说。各有攸当。故来谕中水为包阳之阴。火为包阴之阳及水火无成质而金木有定形。皆已见于朱子说。则朱子既知其如此。而却于图解不用此说。只用阴阳稚盛之说何也。来谕于五行之理。可谓看得出。而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6L 页
 于周子作图之义。朱子解剥之说。看不得。恐当就此商量。不必别求其异也。勉斋论亦以图解稚盛以水金阴火木阳。而下文说水木阳火金阴为可疑。而其所自解。如来谕下段嫩质定形之论耳。
于周子作图之义。朱子解剥之说。看不得。恐当就此商量。不必别求其异也。勉斋论亦以图解稚盛以水金阴火木阳。而下文说水木阳火金阴为可疑。而其所自解。如来谕下段嫩质定形之论耳。精粗本末熊氏及葛翁说。曾所未考。而疑目中只以臆见为说。今蒙指示。继以取舍之论。何敢更为容赘。但疑目引后论中精粗本末字。为分属理气之證。果似牵合。然详其指归。亦为可證之一端。盖其所谓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者。指或者所疑继善成性之不当分阴阳。阴阳太极之不当分道器。以至仁义中正之不当反其类者而统而称之也。其所谓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辨。粲然于其中者。又指继善成性阴阳太极。以至仁义中正之不得不分者而别而称之也。今就或者所疑七条之说而以精粗本末内外宾主字一一准之。则如继成之分阴阳。一物之各一极。只本末字可以略绰分得矣。如仁义中正之分体用而反其类及仁之专言偏言等处。即本末内外宾主等字。可以横贯说过矣。若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体立用行之有先后。则那个精粗本末内外宾主字。无往而说不著矣。岱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7H 页
 镇尝看得如此。故疑目中以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为浑然中粲然者之一。而以精粗本末字。为总断中亦分道器之语。以證其所论。此恐未为无理。然所以为说者太费分疏。有欠简约。谨当削而去之矣。但下教以所谓浑然一致而粲然有分者。直作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之意。且以精粗本末。为说精粗本末之理。此则于后论本指。恐有未尽照勘者。语涉烦蔓。不极所疑。冀赐裁教。
镇尝看得如此。故疑目中以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为浑然中粲然者之一。而以精粗本末字。为总断中亦分道器之语。以證其所论。此恐未为无理。然所以为说者太费分疏。有欠简约。谨当削而去之矣。但下教以所谓浑然一致而粲然有分者。直作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之意。且以精粗本末。为说精粗本末之理。此则于后论本指。恐有未尽照勘者。语涉烦蔓。不极所疑。冀赐裁教。答曰此段所论是非。不敢妄说。来谕以太极阴阳分道器。为浑然中粲然之一。夫浑然中粲然者。道体之本自如是也。太极阴阳分道器者。人之就道器上分别也。今以分道器。为浑然中粲然。则未分看时。却无粲然乎。后论下段曰所谓一源者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则亦是就理上说。恐非分道器说也。来谕每于象理分界。往往混看名义。错用文字。恐于析理处有未尽。然亦安知鄙见正坐此而错认盛见耶。不敢极论。
定之之定曰父子者定则其定在父子矣。曰圣人定之则其定之在圣人矣。其所争虽无多。而恐亦差有分别。且所谓圣人定之者。是定他形生神发。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7L 页
 五性感动。善恶分万事出者而其定之也。在己也定得。在人也定得。故尝以定性定四海之定證之。今复思之。定四海之定。却是粗说。当以易中定民志之定易之。如是说得。伏未知有甚害义。窃意丈席以岱镇将定字作用力著工夫看。故特加辨诲。然岱镇亦未敢作用工夫说。但既有之字则亦须作圣人定之说。且如定性等定字。亦岂强抑定之之谓乎。其工夫却在定字上面耳。
五性感动。善恶分万事出者而其定之也。在己也定得。在人也定得。故尝以定性定四海之定證之。今复思之。定四海之定。却是粗说。当以易中定民志之定易之。如是说得。伏未知有甚害义。窃意丈席以岱镇将定字作用力著工夫看。故特加辨诲。然岱镇亦未敢作用工夫说。但既有之字则亦须作圣人定之说。且如定性等定字。亦岂强抑定之之谓乎。其工夫却在定字上面耳。答曰来谕定之在圣人在己也定得在人也定得许多说。似看定字不出。试就定字更加体思。勿用引譬如何。工夫在定字上。此说亦恐硬涩。
立天之道章。岱镇以对待属阴。流行属阳。此于本章之义。无甚紧关。下教以太费力警之固然矣。然朱子论继善成性之分曰。继之者善。自夫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其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复易。阴之静也以此例之。流行之属阳。对待之属阴。恐亦为自然之象也。至以先对待后流行。为主静之意。则诚为牵强之甚。敢不从教。然图说之首。自动阳而说归静阴。自动静互根而说归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8H 页
 两仪分立。分明是先流行后对待。而至此则却先对待而后流行。其间必有意义。岂可以适然而不之思也。尝试究之。自未有天地之前而言则由其流行之用而对待之体立矣。自既有天地之后而言则即此对待之体而流行之用行矣。正蒙言元气之坱然升降而说归于轻清重浊山川糟粕之成形。此则用起而体立也。中庸言天地之博厚高明而终之以悠久之无彊。此则体立而用行也。以此推之。太极图首。固当说起于流行。而于其终也。亦当以对待为主矣。此其一先一后。自有指归。恐在所辨认也。既承苦苦捏合之警。而复有此苦苦捏合之说。不胜愧恐。
两仪分立。分明是先流行后对待。而至此则却先对待而后流行。其间必有意义。岂可以适然而不之思也。尝试究之。自未有天地之前而言则由其流行之用而对待之体立矣。自既有天地之后而言则即此对待之体而流行之用行矣。正蒙言元气之坱然升降而说归于轻清重浊山川糟粕之成形。此则用起而体立也。中庸言天地之博厚高明而终之以悠久之无彊。此则体立而用行也。以此推之。太极图首。固当说起于流行。而于其终也。亦当以对待为主矣。此其一先一后。自有指归。恐在所辨认也。既承苦苦捏合之警。而复有此苦苦捏合之说。不胜愧恐。答曰前书亦非谓说得不通。而窃覸高明之学。博处尽多而或不免困于所长。故所以奉规者此也。今此来谕。平论义理则固好。而必欲就此章分属则或未知周子之意果出于此耶。大抵看书贵精研。而亦不以凿之使深为得。此在所省念也。
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按既言气阳质阴。而又言动阳静阴。则其意盖以气质皆有动静。而其动即是阳。其静即是阴耳。试就五行形质上观之。如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8L 页
 水之流火之炎。木之敷荣金之割断土之坟起。是动而阳也。如水之止火之伏。木之晦根金之定质土之隤下。是静而阴也。其质如此则其气亦然耳。如此分别。得无悖理否。
水之流火之炎。木之敷荣金之割断土之坟起。是动而阳也。如水之止火之伏。木之晦根金之定质土之隤下。是静而阴也。其质如此则其气亦然耳。如此分别。得无悖理否。答曰说得大槩是。
后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按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为各具一极之喻。似有可疑。盖自一宗而分为许多统。一元而分为十二会言之。则是统体一极之谓。而非各具一极之义也。若曰许多统各有一宗。十二会各有一元。则诸统各具之宗。自有继祢继祖继曾继高之异。而与万物各具之极。初无彼此之别者不同矣。众会各具之元。又非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全。而与万物各具之极。莫非全体之极者有间矣。此未知别有其说耶。
答曰区区看文字粗卤。只以众统之有一宗各会之有一元看。未曾如此细商。然有形之譬例。只略认大义而已。安得无毫釐之差殊。每以皮肤之见。贡愚于研几之下。觉甚悚然。
大学或问小注中以健顺属气。曾承阙疑之诲。今不敢更容浮辩。独当时下教以为健顺字在他处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9H 页
 则可以通理气看。虽彼时以烦聒为嫌。泯默而退。然往往考索之际。不能无掣碍焉。盖健顺二字。始见于易乾坤卦。而程朱子以阳之性阴之性解之。至中庸章句及大学或问。皆以此二字。分属五性。西铭解亦言乾阳坤阴。为天地之气。而乾健坤顺。为天地之志。太极说解所谓阳而健阴而顺。亦以阴阳为气而健顺为其性。凡此皆是说理气大原头处。而其所训解。都只如此。以此观之。设有一二处偶然兼气说。恐当只从此本分定说如何。
则可以通理气看。虽彼时以烦聒为嫌。泯默而退。然往往考索之际。不能无掣碍焉。盖健顺二字。始见于易乾坤卦。而程朱子以阳之性阴之性解之。至中庸章句及大学或问。皆以此二字。分属五性。西铭解亦言乾阳坤阴。为天地之气。而乾健坤顺。为天地之志。太极说解所谓阳而健阴而顺。亦以阴阳为气而健顺为其性。凡此皆是说理气大原头处。而其所训解。都只如此。以此观之。设有一二处偶然兼气说。恐当只从此本分定说如何。答曰健顺之为性。与五常不同。容带气说。庐江时不记有无此言。然果有之则又复妄发矣。承驳示不胜感幸。
诚意之意。彼时辨诲。亦已详矣。然未有一定归结之论。玆复赘焉。盖意之为字。所包固广。不可谓有善而无恶矣。而若论诚意之意则却兼善恶说不透。必作为善去恶好善恶恶之意然后。乃为所当实者耳。故章句既以心之所发训意字。而继之曰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盖曰诚其意者。诚好善诚恶恶以自快足。而不自欠分数也。是则章句之意亦以此意字作好善恶恶说也。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19L 页
 且章句旧本必自慊三字作一于善。而或问仍其说则其属之善一边尤分明矣。辨诲以归之善一边者为偏而不弘。恐在所商量也。如何如何。
且章句旧本必自慊三字作一于善。而或问仍其说则其属之善一边尤分明矣。辨诲以归之善一边者为偏而不弘。恐在所商量也。如何如何。答曰诚意之为生死关。以其为善恶几也。若心之所发。只有善而无恶。只著一个为善字足矣。何用更说去恶耶。故曰此意字阔包善恶好恶看。不必分情与意为两物。未知如何。
心统性情之义。曾于讲座中略贡愚见而未蒙察纳。至与柳濯叟诸人屡言而不合。当时说话。今不能一一记得。然大槩岱镇则谓统字当作统理统御等统字看。至引程林隐图说中心不统性则无以致未发之中。心不统情则无以致中节之和之说以證之。丈席则谓统字不必作有力看。只当作包该意看。虽用盛贮该载。敷施发用等语。亦轻轻地说过。至以杯碗之盛水注水譬之。而濯叟诸人便以合理气之合字释统字。岱镇只得抱疑而不能屈而已。其后考朱子语则有曰统是主宰。若与愚见合者然后。始以前日之不能屈。为不足深罪。而谨复略陈其愚。冀卒当日之教。大抵心也性也情也。非有各件物也。只心之理为性。心之发为情。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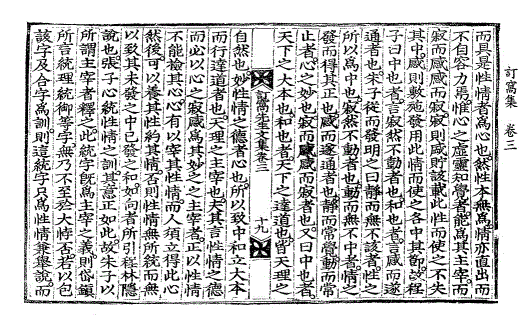 而具是性情者为心也。然性本无为。情亦直出而不自容力焉。惟心之虚灵知觉者。能为其主宰。而寂而感感而寂。寂则盛贮该载此性而使之不失其中。感则敷施发用此情而使之各中其节。故程子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朱子从而发明之曰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寂然不动者也。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夫其言性情之德而必以心之寂感为其妙之之主宰者。正以性情不能检其心。心有以宰其性情。而人须立得此心然后。可以养其性约其情。否则性情无所统而无以致其未发之中已发之和。如向者所引程林隐说也。张子心统性情之训。其意正如此。故朱子以所谓主宰者释之。此统字既为主宰之义。则岱镇所言统理统御等字。无乃不至于大悖否。若以包该字及合字为训。则这统字只为性情兼举说。而
而具是性情者为心也。然性本无为。情亦直出而不自容力焉。惟心之虚灵知觉者。能为其主宰。而寂而感感而寂。寂则盛贮该载此性而使之不失其中。感则敷施发用此情而使之各中其节。故程子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朱子从而发明之曰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寂然不动者也。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夫其言性情之德而必以心之寂感为其妙之之主宰者。正以性情不能检其心。心有以宰其性情。而人须立得此心然后。可以养其性约其情。否则性情无所统而无以致其未发之中已发之和。如向者所引程林隐说也。张子心统性情之训。其意正如此。故朱子以所谓主宰者释之。此统字既为主宰之义。则岱镇所言统理统御等字。无乃不至于大悖否。若以包该字及合字为训。则这统字只为性情兼举说。而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0L 页
 不为心之主宰说矣。其于张朱之意何如也。至以杯碗之盛水注水为喻。则又似以心之统性情者。只作块然一物。而静无所主。动无所宰者然。恐亦非虚灵知觉具众理应万事者之本然面目也。岱镇妄窃验之于躬。凡日用之间。静则昏昧放倒而不见所谓未发之体。动则纷纠舛戾而未见其有中节之时。既以追求其故。则直以主心不定。不能统而宰之。任其自动而自息耳。然后知心统性情四字。所以示人之意直是明白亲切。又知古人一敬字。都为统字上要妙工夫。而独未能以身体究耳。此言固近于倡家之礼佛。而其于统字之意。亦似窥得一斑。伏望恕其僭而攻其疵。无使徒疑而无所正也。
不为心之主宰说矣。其于张朱之意何如也。至以杯碗之盛水注水为喻。则又似以心之统性情者。只作块然一物。而静无所主。动无所宰者然。恐亦非虚灵知觉具众理应万事者之本然面目也。岱镇妄窃验之于躬。凡日用之间。静则昏昧放倒而不见所谓未发之体。动则纷纠舛戾而未见其有中节之时。既以追求其故。则直以主心不定。不能统而宰之。任其自动而自息耳。然后知心统性情四字。所以示人之意直是明白亲切。又知古人一敬字。都为统字上要妙工夫。而独未能以身体究耳。此言固近于倡家之礼佛。而其于统字之意。亦似窥得一斑。伏望恕其僭而攻其疵。无使徒疑而无所正也。答曰所论此心主宰统理之说。义理明白。议论切实。真可谓目下受用之资。不胜叹仰。所贵乎心统性情者。欲其如此而已。夫孰曰不可。但张子所谓心统性情者。只是平说心之情状。未便遽及于工夫上。凡圣贤说心。皆包出入兼存亡。并谓之神明不测之妙。张子之意亦若是而已。心是主宰之物。上而盛贮此性。下而敷施此情。这便是主宰。故朱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1H 页
 子曰统是主宰。盖言其为动静寂感之主也。今以静而使之不失其中。动而使之各中其节然后为统字之义。则圣贤说只此一统字足矣。更何用许多工夫也。杯碗盛注之喻。只可略绰认取。未必一一恰同。然自杯碗而言之则盛之者杯碗之量也。注之者杯碗之能也。岂但为块然无用之赘物乎。来谕静而昏昧放倒。动而纷纠舛戾。则主心不定不能统其性情。任其自动自息云。未知自动自息者。是性情之自动自息而心无与焉耶。抑此等人之心。不可谓统性情。而必时中者之心然后方可用此训释耶。若其工夫节度。当如来谕耳。
子曰统是主宰。盖言其为动静寂感之主也。今以静而使之不失其中。动而使之各中其节然后为统字之义。则圣贤说只此一统字足矣。更何用许多工夫也。杯碗盛注之喻。只可略绰认取。未必一一恰同。然自杯碗而言之则盛之者杯碗之量也。注之者杯碗之能也。岂但为块然无用之赘物乎。来谕静而昏昧放倒。动而纷纠舛戾。则主心不定不能统其性情。任其自动自息云。未知自动自息者。是性情之自动自息而心无与焉耶。抑此等人之心。不可谓统性情。而必时中者之心然后方可用此训释耶。若其工夫节度。当如来谕耳。知字之说。向蒙提诲。犹未释然。玆复仰叩焉。下教谓知觉之知。即四德之知。而四德之知为体。知觉之知为用。此固一说也。朱子尝于仁说之末。以知觉为知之事。又曰觉是知之用。此即丈席之说也。然朱子之所以为说者。其意自别。盖为论仁者以觉为训。故明其非是而取其苗脉之所因。义类之所近。以为当属之此。盖即说者所将训仁之一端而言之。非槩以虚灵知觉者。便作四德之知之用也。今就四德之知知觉之知两知字而论之。则岂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1L 页
 可以苗脉义类之似而遂无所辨别哉。夫知觉者何也。心之主乎一身而其虚灵之妙。自能随触而感喻者也。知者何也。性之具于是心而其贞固之德。足以干事而分别者也。是则两知字虽是一字。而其所指而名之者。已自不同也。故朱子曰知是分别是非底道理。曰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夫知为理之本然。而知觉为气之所能。则是其有道器之分也。先儒曰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仁义礼智信也。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夫知为性之一德。而知觉为心之总用。则是其有偏全之异也。(全专字之误。)朱子曰心之知觉一而已。而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又曰知觉运动。人与物同。而仁义礼智之粹然者。非物之所得而全。夫知为性命之粹然。而知觉为从气从性及万物蠢动者之所通称。则此又其精粗纯杂之别也。故言知则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盖知其体而所谓是非者其用也。言知觉则自虚灵说来。盖知觉其用而所谓虚灵者其体也。但知之发也。亦须知之觉之。而知觉之前。须有知觉之理。故知之用。不能外乎知觉。知觉之体。不能离乎知。然
可以苗脉义类之似而遂无所辨别哉。夫知觉者何也。心之主乎一身而其虚灵之妙。自能随触而感喻者也。知者何也。性之具于是心而其贞固之德。足以干事而分别者也。是则两知字虽是一字。而其所指而名之者。已自不同也。故朱子曰知是分别是非底道理。曰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夫知为理之本然。而知觉为气之所能。则是其有道器之分也。先儒曰人之所以为性者五。仁义礼智信也。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夫知为性之一德。而知觉为心之总用。则是其有偏全之异也。(全专字之误。)朱子曰心之知觉一而已。而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又曰知觉运动。人与物同。而仁义礼智之粹然者。非物之所得而全。夫知为性命之粹然。而知觉为从气从性及万物蠢动者之所通称。则此又其精粗纯杂之别也。故言知则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盖知其体而所谓是非者其用也。言知觉则自虚灵说来。盖知觉其用而所谓虚灵者其体也。但知之发也。亦须知之觉之。而知觉之前。须有知觉之理。故知之用。不能外乎知觉。知觉之体。不能离乎知。然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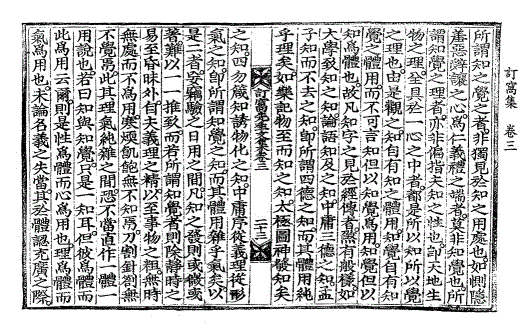 所谓知之觉之者。非独见于知之用处也。如恻隐羞恶辞让之心。为仁义礼之端者。莫非知觉也。所谓知觉之理者。亦非偏指夫知之性也。即天地生物之理。全具于一心之中者。都是所以知所以觉之理也。由是观之。知自有知之体用。知觉自有知觉之体用。而不可言知但以知觉为用。知觉但以知为体也。故凡知字之见于经传者。煞有般样。如大学致知之知。论语知及之知。中庸三德之知。孟子知而不去之知。即所谓四德之知。而其体用纯乎理矣。如乐记物至而知之知。太极图神发知矣之知。四勿箴知诱物化之知。中庸序从义理从形气之知。即所谓知觉之知。而其体用杂乎气矣。以是二者。妄窃验之日用之间。凡知之发则或微或著。难以一一推致。而若所谓知觉者则除静时之易至昏昧外。自夫义理之精。以至事物之粗。无时无处而不为用。寒暖饥饱无不知焉。刀割针劄无不觉焉。此其理气纯杂之间。恐不当直作一体一用说也。若曰知与知觉。只是一知耳。但彼为体而此为用云尔。则是性为体而心为用也。理为体而气为用也。未论名义之失当。其于体认充广之际。
所谓知之觉之者。非独见于知之用处也。如恻隐羞恶辞让之心。为仁义礼之端者。莫非知觉也。所谓知觉之理者。亦非偏指夫知之性也。即天地生物之理。全具于一心之中者。都是所以知所以觉之理也。由是观之。知自有知之体用。知觉自有知觉之体用。而不可言知但以知觉为用。知觉但以知为体也。故凡知字之见于经传者。煞有般样。如大学致知之知。论语知及之知。中庸三德之知。孟子知而不去之知。即所谓四德之知。而其体用纯乎理矣。如乐记物至而知之知。太极图神发知矣之知。四勿箴知诱物化之知。中庸序从义理从形气之知。即所谓知觉之知。而其体用杂乎气矣。以是二者。妄窃验之日用之间。凡知之发则或微或著。难以一一推致。而若所谓知觉者则除静时之易至昏昧外。自夫义理之精。以至事物之粗。无时无处而不为用。寒暖饥饱无不知焉。刀割针劄无不觉焉。此其理气纯杂之间。恐不当直作一体一用说也。若曰知与知觉。只是一知耳。但彼为体而此为用云尔。则是性为体而心为用也。理为体而气为用也。未论名义之失当。其于体认充广之际。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2L 页
 无乃亦有所妨乎。七情中喜怒爱恶。谓之发于仁义可也。而朱子但言其有相似处。而未尝便作仁义之用者。正以杂气者不得为纯理之用也。况知自是性。知觉自是心。其分又异于性之与情者乎。向日辨诲中。虽有纯理合气之辨。而其曰单说知觉而论其体用则虚灵为体知觉为用。而对四德之知则虚灵知觉并属之用者。终似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而至以诸侯之君。自于其国为君臣。而对天子则并为之臣为譬。则又似心不能为性之主宰。而性反为心之主宰。恐于心统性情之义。未免有抵捂耳。疑晦之极。敢此烦冒。伏惟有以终教之也。
无乃亦有所妨乎。七情中喜怒爱恶。谓之发于仁义可也。而朱子但言其有相似处。而未尝便作仁义之用者。正以杂气者不得为纯理之用也。况知自是性。知觉自是心。其分又异于性之与情者乎。向日辨诲中。虽有纯理合气之辨。而其曰单说知觉而论其体用则虚灵为体知觉为用。而对四德之知则虚灵知觉并属之用者。终似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而至以诸侯之君。自于其国为君臣。而对天子则并为之臣为譬。则又似心不能为性之主宰。而性反为心之主宰。恐于心统性情之义。未免有抵捂耳。疑晦之极。敢此烦冒。伏惟有以终教之也。答曰夫道理之在人心。非有形色䫉象各占窠窟。只是得天地之理气合而为心。而其情状则虚灵也。其技能则知觉也。圣人就此虚灵知觉上欲指示其本原。故剔其纯理者而谓之仁义礼智。指其因是性而发见者而谓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然则仁义礼智。即虚灵之实体。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者。即知觉之件数也。纯理曰性。合理气曰心。而即此合理之理。与纯理之理。初无二理。则纯理曰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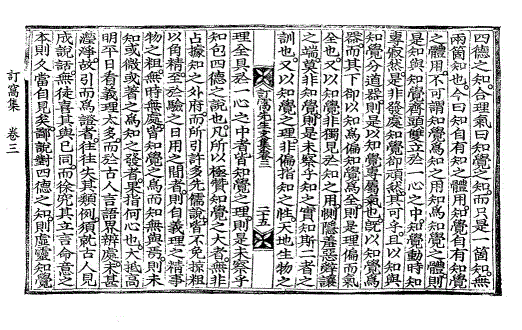 四德之知。合理气曰知觉之知。而只是一个知。无两个知也。今曰知自有知之体用。知觉自有知觉之体用。不可谓知觉为知之用知为知觉之体。则是知与知觉齐头双立于一心之中。知觉动时知专寂然。是非发处知觉却顽然。其可乎。且以知与知觉分道器。则是以知觉专属气也。既以知觉为器。而其下却以知为偏知觉为全。则是理偏而气全也。又以知觉非独见于知之用。恻隐羞恶辞让之端。莫非知觉。则是未察乎知之实知斯二者之训也。又以知觉之理。非偏指知之性。天地生物之理全具于一心之中者皆知觉之理。则是未察乎知包四德之说也。凡所以极赞知觉之大者。无非占据知之外府。而所引许多先儒说。皆不免掠粗以角精。至于验之日用之间者。则自义理之精事物之粗。无时无处。皆知觉之为而知无与焉。则未知或微或著之为知之发者。果指何心也。大抵高明平日看义理太多。而于古人言语界辨处。未甚滢净。故引而为證者。往往失其类例。须就古人见成说话。无徒喜其与己同。而徐究其立言命意之本则久当自见矣。鄙说对四德之知。则虚灵知觉
四德之知。合理气曰知觉之知。而只是一个知。无两个知也。今曰知自有知之体用。知觉自有知觉之体用。不可谓知觉为知之用知为知觉之体。则是知与知觉齐头双立于一心之中。知觉动时知专寂然。是非发处知觉却顽然。其可乎。且以知与知觉分道器。则是以知觉专属气也。既以知觉为器。而其下却以知为偏知觉为全。则是理偏而气全也。又以知觉非独见于知之用。恻隐羞恶辞让之端。莫非知觉。则是未察乎知之实知斯二者之训也。又以知觉之理。非偏指知之性。天地生物之理全具于一心之中者皆知觉之理。则是未察乎知包四德之说也。凡所以极赞知觉之大者。无非占据知之外府。而所引许多先儒说。皆不免掠粗以角精。至于验之日用之间者。则自义理之精事物之粗。无时无处。皆知觉之为而知无与焉。则未知或微或著之为知之发者。果指何心也。大抵高明平日看义理太多。而于古人言语界辨处。未甚滢净。故引而为證者。往往失其类例。须就古人见成说话。无徒喜其与己同。而徐究其立言命意之本则久当自见矣。鄙说对四德之知。则虚灵知觉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3L 页
 并属之用云者。谓之属之用则亦非直以为用如性情之说也。言其知为本原而知觉属乎用一边也。然亦非敢自是。如有未当。更赐反复如何。
并属之用云者。谓之属之用则亦非直以为用如性情之说也。言其知为本原而知觉属乎用一边也。然亦非敢自是。如有未当。更赐反复如何。上所庵先生
顷因杏亭之会。得蹑舆马之尘。几一旬矣。第其人事稠沓。苦无间隙。每于候谒之际。仅得望颜色问寒温而退。凡畴日之所蕴藏于中者。一未得开口仰讨。及其治任之日。则又不得临歧而面辞。区区慊怅。殆累日而不释也。仄闻彼时徒驭。迤向林岭。不审返定今几日。而燕养节宣复何如。伏想山北新庵。琴书整暇。日与二三秀才。讲磨其中。益令人向往而不能已也。岱镇跋履海山。积抱困惫。归后又以老人愆度。忧闵度日。因循汩没之中。试一点检身里。凡向之耳剽而口窃者。亦已涣散而无馀矣。况望其进于此而有所持循耶。此际窃欲得大方一言。以激其颓塌之气。玆复就前日往复之说。更具疑目。以为求教之梯。幸无以烦猥而退斥之也。
问目
阴阳稚盛之说。近考退溪答李公浩问目曰。以生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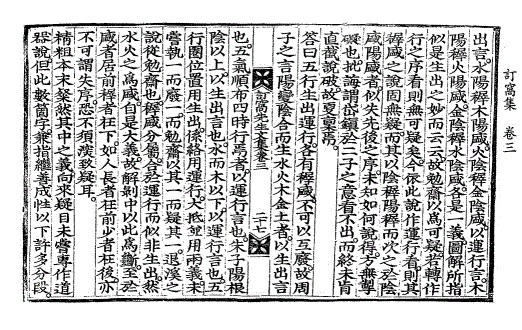 出言。水阳稚木阳盛。火阴稚金阴盛。以运行言。木阳稚火阳盛。金阴稚水阴盛。各是一义。图解所指似是生出之妙而云云。故勉斋以为可疑。若转作行之序看则无可疑矣。今依此说作运行看。则其稚盛之说固无疑。而其以阴稚阳稚而次之于阴盛阳盛者。似失先后之序。未知如何说得。方无掣碍也。批诲谓岱镇于二子之意看不出。而终未肯直截说破。故更禀焉。
出言。水阳稚木阳盛。火阴稚金阴盛。以运行言。木阳稚火阳盛。金阴稚水阴盛。各是一义。图解所指似是生出之妙而云云。故勉斋以为可疑。若转作行之序看则无可疑矣。今依此说作运行看。则其稚盛之说固无疑。而其以阴稚阳稚而次之于阴盛阳盛者。似失先后之序。未知如何说得。方无掣碍也。批诲谓岱镇于二子之意看不出。而终未肯直截说破。故更禀焉。答曰五行生出运行。各有稚盛。不可以互废。故周子之言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以生出言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者。以运行言也。朱子阳根阴以上。以生出言也。水而木以下。以运行言也。五行圈位置用生出。系络用运行。大抵并用两义。未尝执一而废一。而勉斋以其一而疑其一。退溪之说从勉斋也。稚盛分属。合于运行而似非生出。然水火之为盛。自是大义。故解剥中以此为断。至于盛者居前稚者在下。如人长者在前少者在后。亦不可谓失序。恐不须深致疑耳。
精粗本末粲然其中之义。向来疑目未尝专作道器说。但此数个字。兼指继善成性以下许多分段。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4L 页
 而道器之分。亦该在中间。故就其中剔出而言之。以为此数字亦可以分属道器。此其为图解精粗字之證。固不免劳攘。而其于后论本指。似不至大悖矣。批诲以混看名义。错用文字警之。岂其以本文道体二字。直以道说起。而今以道器之分。参错为说。则有夹杂之病云耶。圣贤之言道体亦有般样。固有直指其本体之妙而言者矣。亦有统指其全体之备而言者矣。语其本体之妙则固不当杂器而言。而若语夫全体之备则如程子所谓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者。何尝不合器与道而总谓之道体耶。今此后论所谓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粲然其中者。乃指继善成性。太极阴阳。体用显微之类而分合为说。则所谓本体之妙全体之备。都包在其中矣。是则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何独不为浑然中之粲然者乎。批诲曰浑然而粲然者。道体之本自如是也。太极阴阳分道器者。人之就道器上分别也。今以分道器为浑然中粲然。则未分看时却无粲然乎。此则似以道器之分。为本不如此。而必待人旋安排去分别
而道器之分。亦该在中间。故就其中剔出而言之。以为此数字亦可以分属道器。此其为图解精粗字之證。固不免劳攘。而其于后论本指。似不至大悖矣。批诲以混看名义。错用文字警之。岂其以本文道体二字。直以道说起。而今以道器之分。参错为说。则有夹杂之病云耶。圣贤之言道体亦有般样。固有直指其本体之妙而言者矣。亦有统指其全体之备而言者矣。语其本体之妙则固不当杂器而言。而若语夫全体之备则如程子所谓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者。何尝不合器与道而总谓之道体耶。今此后论所谓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粲然其中者。乃指继善成性。太极阴阳。体用显微之类而分合为说。则所谓本体之妙全体之备。都包在其中矣。是则太极阴阳之分道器。何独不为浑然中之粲然者乎。批诲曰浑然而粲然者。道体之本自如是也。太极阴阳分道器者。人之就道器上分别也。今以分道器为浑然中粲然。则未分看时却无粲然乎。此则似以道器之分。为本不如此。而必待人旋安排去分别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5H 页
 然后方有分别者然。尤岱镇之所惑也。果未知道器之分。真以人之看不看而有所异同耶。若使其意但为合看则不相离。而分看则不相杂。则理中之浑然粲然者。亦何以异于是哉。伏望更就后论中一一勘准然后。一言教破。则敢不濯旧而来新焉。
然后方有分别者然。尤岱镇之所惑也。果未知道器之分。真以人之看不看而有所异同耶。若使其意但为合看则不相离。而分看则不相杂。则理中之浑然粲然者。亦何以异于是哉。伏望更就后论中一一勘准然后。一言教破。则敢不濯旧而来新焉。答曰浑然而粲然者。一物而有分合也。道器者。两物而有界辨也。向来盛谕以道器为浑然中粲然。故有所奉复。今承驳示。敢不致思。然前辈合器与道而总谓之道体者。皆指器之理而言。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为五达道。岂以君臣父子形而下者为道耶。程子此条亦恐非指器为道体。大抵此理至微。不可以夹杂说。而来谕每于象理分界处。往往有混看。故前日奉疑者此耳。鄙说未分看时却无粲然一转。承此驳论。不胜瞿然。然未有此物。先有此理。而此理之中。已具粲然。不必待有器而后为粲然。如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无眹之时。何尝有象。而象之理已粲然矣。岂可以森然之故。而便谓万象之器。并萃于冲漠中耶。更乞裁教。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5L 页
 众统之同一宗。各会之同一元。只为万物同一极之喻。而于一物各一极之义。终不相当。未知别有其说耶。
众统之同一宗。各会之同一元。只为万物同一极之喻。而于一物各一极之义。终不相当。未知别有其说耶。答曰有形之譬。何能节节符合。此统不假于彼而宗自有。此会不夺于彼而元自足。则亦可认取。区区别无他说。
诚意之说。前书略已證明。而更参或问。其义尤的然。其曰心之所发。如曰好善则必由中及外无一毫之不好。如曰恶恶则必由中及外无一毫之不恶云者。分明将此意字作好善恶恶说。而于诚意工夫无不尽。于诚意训释无不明。外此而更撰不得矣。伏请将此更入思议如何。
答曰向来诸说。或偏执好恶。或偏执善恶。分情分意。争说纷纭。故僭谓不分情意。只心之发皆意云者。盖通指善恶好恶之意耳。何但或问。传文如好如恶。独非好善恶恶耶。来谕似错认鄙本意。
心统性情之说。批诲往往以愚见为可采。而其论张子本指处。终有不能无疑者。岂迷滞之见。自阻于平易之教耶。批诲曰心统性情者。只是平说心之情状。圣贤说心。皆包出入兼存亡而并谓之神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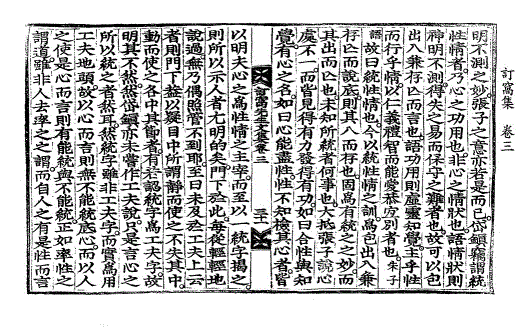 明不测之妙。张子之意亦若是而已。岱镇窃谓统性情者。乃心之功用也。非心之情状也。语情状则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者也。故可以包出入兼存亡而言也。语功用则虚灵知觉。主乎性而行乎情。以仁义礼智而能爱恭宜别者也。(朱子语。)故曰统性情也。今以统性情之训。为包出入兼存亡而说底。则其入而存也。固为有统之之妙。而其出而亡也。未知所统者何事也。大抵张子说心处不一。而皆见得有力发得有功。如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如曰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者。皆以明夫心之为性情之主宰。而至以一统字揭之。则所以示人者尤明的矣。门下于此。每从轻轻地说过。无乃偶照管不到耶。至曰未及于工夫上云者则门下盖以疑目中所谓静而使之不失其中。动而使之各中其节者。有若认统字为工夫字。故明其不然。然岱镇亦未尝作工夫说。只是言心之所以统之者然耳。然统字虽非工夫字。而实为用工夫地头。故以心而言则无不能统底心。而以人之使是心而言则有能统与不能统。正如率性之谓道。虽非人去率之之谓。而自人之有是性而言
明不测之妙。张子之意亦若是而已。岱镇窃谓统性情者。乃心之功用也。非心之情状也。语情状则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者也。故可以包出入兼存亡而言也。语功用则虚灵知觉。主乎性而行乎情。以仁义礼智而能爱恭宜别者也。(朱子语。)故曰统性情也。今以统性情之训。为包出入兼存亡而说底。则其入而存也。固为有统之之妙。而其出而亡也。未知所统者何事也。大抵张子说心处不一。而皆见得有力发得有功。如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如曰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者。皆以明夫心之为性情之主宰。而至以一统字揭之。则所以示人者尤明的矣。门下于此。每从轻轻地说过。无乃偶照管不到耶。至曰未及于工夫上云者则门下盖以疑目中所谓静而使之不失其中。动而使之各中其节者。有若认统字为工夫字。故明其不然。然岱镇亦未尝作工夫说。只是言心之所以统之者然耳。然统字虽非工夫字。而实为用工夫地头。故以心而言则无不能统底心。而以人之使是心而言则有能统与不能统。正如率性之谓道。虽非人去率之之谓。而自人之有是性而言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6L 页
 则有能率与不能率。故疑目以众人之静而昏昧动而纷扰。为不能统性情之病。而既不能统性情。则其性情动静之际。其心自由。(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无以约其情养其性。故直谓之任其自动而自息。批诲反之曰众人之心。不可谓统性情耶。自动自息者。心无与焉耶。岱镇固谓众人虽有统性情底心。而自不能统性情矣。而乃若自动自息者。亦语夫心之不宰耳。性情之动静。即心之动静。则乌可曰无与焉耶。朱子答南轩书曰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动。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此陋说之所本也。或者其寡过耶。舛谬之见。过自分疏。惟赐裁教。
则有能率与不能率。故疑目以众人之静而昏昧动而纷扰。为不能统性情之病。而既不能统性情。则其性情动静之际。其心自由。(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无以约其情养其性。故直谓之任其自动而自息。批诲反之曰众人之心。不可谓统性情耶。自动自息者。心无与焉耶。岱镇固谓众人虽有统性情底心。而自不能统性情矣。而乃若自动自息者。亦语夫心之不宰耳。性情之动静。即心之动静。则乌可曰无与焉耶。朱子答南轩书曰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动。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此陋说之所本也。或者其寡过耶。舛谬之见。过自分疏。惟赐裁教。答曰心该动静。而静为性动为情。故曰心统性情。若因是言而究言之。则动静之得其正。谓之有统。不得其正者。谓之无统可也。而原初立名之义。何尝偏指得正而言之耶。来谕以心而言则无不能统底心。而以人之使是心而言则有能统与不能统云者固是。而张子此说即所谓以心而言者也。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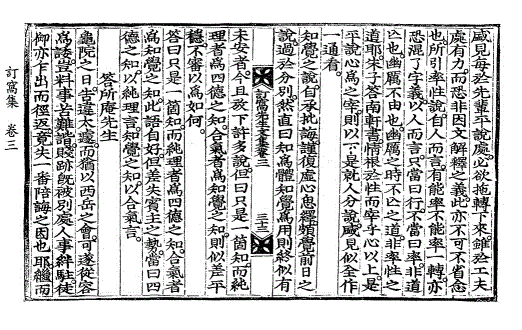 盛见每于先辈平说处。必欲拖转下来。虽于工夫处有力。而恐非因文解释之义。此亦不可不省念也。所引率性说。自人而言。有能率不能率一转。亦恐混了字义。以人而言。只当曰行。不当曰率。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幽厉之时不亡之道。非率性之道耶。朱子答南轩书。情根于性而宰乎心以上。是平说心为之宰。则以下是就人分说。盛见似全作一通看。
盛见每于先辈平说处。必欲拖转下来。虽于工夫处有力。而恐非因文解释之义。此亦不可不省念也。所引率性说。自人而言。有能率不能率一转。亦恐混了字义。以人而言。只当曰行。不当曰率。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幽厉之时不亡之道。非率性之道耶。朱子答南轩书。情根于性而宰乎心以上。是平说心为之宰。则以下是就人分说。盛见似全作一通看。知觉之说。自承批诲。谨复虚心思绎。颇觉前日之说。过于分别。然直曰知为体知觉为用则终似有未安者。今且放下许多说。但曰只是一个知。而纯理者为四德之知。合气者为知觉之知。则似差平稳。不审以为如何。
答曰只是一个知。而纯理者为四德之知。合气者为知觉之知。此语自好。但差失宾主之势。当曰四德之知。以纯理言。知觉之知。以合气言。
答所庵先生
龟院之日。告违太遽。而犹以西岳之会。可遂从容为诿。岂料事苦难谐。贱迹既被别处人事绊驻。徒御亦乍出而径返。竟失一番陪诲之因也耶。继而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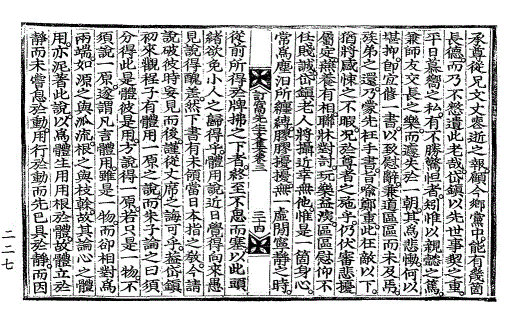 承尊从兄文丈丧逝之报。顾今乡党中。能有几个长德。而乃不慭遗此老哉。岱镇以先世事契之重。平日慕向之私。有不胜惊怛者。矧惟以亲懿之笃。兼师友交长之乐。而遽失于一朝。其为悲恸。何以堪抑。即宜修一书。以致慰辞。兼道区区而未及焉。族弟之还。乃蒙先枉手书。旨喻郑重。此在敌以下。犹将感悚之不暇。况于尊者之施乎。仍伏审悲扰属定。燕养有相。联床对讨。玩乐益深。区区慰仰不任贱诚。岱镇老人将摄近幸无他。惟是一个身心。常为尘汩所缠缚。胶胶扰扰。无一虚閒宁静之时。从前所得于牌拂之下者。终至不思而塞。以此头绪欲免小人之归得乎。体用说近日觉得向来愚见说得丑差。然下书有未领当日本指之教。今请说破彼时妄见而后。谨从丈席之诲可乎。盖岱镇初来观程子有体用一原之说。而朱子论之曰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方说得一原。若只是一物。不须说一原。遂谓凡言体用。虽是一物。而却相对为两端。如源之与派流。根之与枝干。故其论心之体用。亦泥著此说。以为体生用用根于体。故体立于静而未尝息于动。用行于动而先已具于静。而因
承尊从兄文丈丧逝之报。顾今乡党中。能有几个长德。而乃不慭遗此老哉。岱镇以先世事契之重。平日慕向之私。有不胜惊怛者。矧惟以亲懿之笃。兼师友交长之乐。而遽失于一朝。其为悲恸。何以堪抑。即宜修一书。以致慰辞。兼道区区而未及焉。族弟之还。乃蒙先枉手书。旨喻郑重。此在敌以下。犹将感悚之不暇。况于尊者之施乎。仍伏审悲扰属定。燕养有相。联床对讨。玩乐益深。区区慰仰不任贱诚。岱镇老人将摄近幸无他。惟是一个身心。常为尘汩所缠缚。胶胶扰扰。无一虚閒宁静之时。从前所得于牌拂之下者。终至不思而塞。以此头绪欲免小人之归得乎。体用说近日觉得向来愚见说得丑差。然下书有未领当日本指之教。今请说破彼时妄见而后。谨从丈席之诲可乎。盖岱镇初来观程子有体用一原之说。而朱子论之曰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方说得一原。若只是一物。不须说一原。遂谓凡言体用。虽是一物。而却相对为两端。如源之与派流。根之与枝干。故其论心之体用。亦泥著此说。以为体生用用根于体。故体立于静而未尝息于动。用行于动而先已具于静。而因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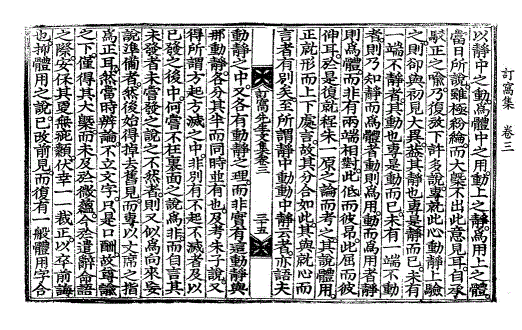 以静中之动。为体中之用。动上之静。为用上之体。当日所说。虽极纷纶。而大槩不出此意见耳。自承驳正之喻。乃复放下许多说。专就此心动静上验之。则却与初见大异。盖其静也专是静而已。未有一端不静者。其动也专是动而已。未有一端不动者。则乃知静而为体者动则为用。动而为用者静则为体。而非有两端相对。此低而彼昂。此屈而彼伸耳。于是复就程朱一原之论而考之。其说体用。正就形而上下处言。故其分合如此。其与就心而言者有别矣。至所谓静中动动中静云者。亦语夫动静之中。又各有动静之理。而非实有这动静与那动静。各分其半而同时并有也。及考朱子说。又得所谓方起方灭之中。非别有不起不灭者及以已发之后中。何尝不在里面之说为非。而自言其未发者未尝发之说之不然者。则又似为向来妄说准备者。然后始得掉去旧见。而专以丈席之指为正耳。然当时辨论。不立文字。只是口酬。故尊谕之下。仅得其大槩。而未及于微蕴。今于遣辞命语之际。安保其更无疵颣。伏幸一一裁正。以卒前诲也。抑体用之说。已改前见。而复有一般体用字合
以静中之动。为体中之用。动上之静。为用上之体。当日所说。虽极纷纶。而大槩不出此意见耳。自承驳正之喻。乃复放下许多说。专就此心动静上验之。则却与初见大异。盖其静也专是静而已。未有一端不静者。其动也专是动而已。未有一端不动者。则乃知静而为体者动则为用。动而为用者静则为体。而非有两端相对。此低而彼昂。此屈而彼伸耳。于是复就程朱一原之论而考之。其说体用。正就形而上下处言。故其分合如此。其与就心而言者有别矣。至所谓静中动动中静云者。亦语夫动静之中。又各有动静之理。而非实有这动静与那动静。各分其半而同时并有也。及考朱子说。又得所谓方起方灭之中。非别有不起不灭者及以已发之后中。何尝不在里面之说为非。而自言其未发者未尝发之说之不然者。则又似为向来妄说准备者。然后始得掉去旧见。而专以丈席之指为正耳。然当时辨论。不立文字。只是口酬。故尊谕之下。仅得其大槩。而未及于微蕴。今于遣辞命语之际。安保其更无疵颣。伏幸一一裁正。以卒前诲也。抑体用之说。已改前见。而复有一般体用字合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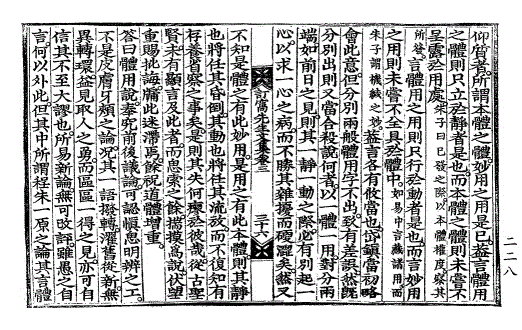 仰质者。所谓本体之体。妙用之用是已。盖言体用之体则只立于静者是也。而本体之体则未尝不呈露于用处。(朱子曰已发之际。以本体权度。察其所发。)言体用之用则只行于动者是也。而言妙用之用则未尝不全具于体中。(如易中言藏诸用。而朱子谓机缄之妙。)盖言各有攸当也。岱镇当初略会此意。但分别两般体用字不出。致有差误。然既分别出则又当合杀说何者。以一体一用。对分两端。如前日之见。则其一静一动之际。必有别起一心。以求一心之病。而不胜其杂扰而硬涩矣。然又不知是体之有此妙用。是用之有此本体。则其静也将任其昏倒。其动也将任其流放。而不复知有存养省察之事矣。是则其失何瘳于彼哉。从古圣贤。未有显言及此者。而思索之馀。揣摸为说。伏望重赐批诲。牖此迷滞焉。馀祝道体增重。
仰质者。所谓本体之体。妙用之用是已。盖言体用之体则只立于静者是也。而本体之体则未尝不呈露于用处。(朱子曰已发之际。以本体权度。察其所发。)言体用之用则只行于动者是也。而言妙用之用则未尝不全具于体中。(如易中言藏诸用。而朱子谓机缄之妙。)盖言各有攸当也。岱镇当初略会此意。但分别两般体用字不出。致有差误。然既分别出则又当合杀说何者。以一体一用。对分两端。如前日之见。则其一静一动之际。必有别起一心。以求一心之病。而不胜其杂扰而硬涩矣。然又不知是体之有此妙用。是用之有此本体。则其静也将任其昏倒。其动也将任其流放。而不复知有存养省察之事矣。是则其失何瘳于彼哉。从古圣贤。未有显言及此者。而思索之馀。揣摸为说。伏望重赐批诲。牖此迷滞焉。馀祝道体增重。答曰体用说。奉究前后议论。可认慎思明辨之工。不是皮肤牙颊之论。况其一语拨转。濯旧从新。无异转环。益见取人之勇。而区区一得之见。亦可自信其不至大谬也。所易新论。无可改评。虽愚之自言。何以外此。但其中所谓程朱一原之论其言体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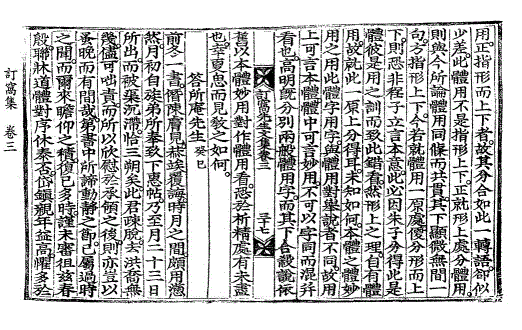 用。正指形而上下者。故其分合如此一转语。却似少差。此体用不是指形上下。正就形上处分体用。则与今所论体用同条而共贯。其下显微无间一句。方指形上下。今若就体用一原处。便分形而上下。则恐非程子立言本意。此必因朱子分得此是体彼是用之训而致此错看。然形上之理。自有体用。故就此一原上分得耳。未知如何。本体之体妙用之用此体字用字。与体用对举说者不同。故用上可言本体。体中可言妙用。不可以字同而混并看也。高明既分别两般体用字。而其下合杀说依旧以本体妙用对作体用看。恐于析精处有未尽也。幸更思而见教之如何。
用。正指形而上下者。故其分合如此一转语。却似少差。此体用不是指形上下。正就形上处分体用。则与今所论体用同条而共贯。其下显微无间一句。方指形上下。今若就体用一原处。便分形而上下。则恐非程子立言本意。此必因朱子分得此是体彼是用之训而致此错看。然形上之理。自有体用。故就此一原上分得耳。未知如何。本体之体妙用之用此体字用字。与体用对举说者不同。故用上可言本体。体中可言妙用。不可以字同而混并看也。高明既分别两般体用字。而其下合杀说依旧以本体妙用对作体用看。恐于析精处有未尽也。幸更思而见教之如何。答所庵先生(癸巳)
前冬一书。僭陈肤见。恭俟覆诲。时月之间。颇用懑然。月初自族弟所奉致下惠帖。乃至月二十三日所出。而被渠沉滞。恰三朔矣。此君疏脱。去洪乔无几。尽可咄责。而所以欣慰于承领之后。则亦岂以蚤晚而有间哉。第书中所谛动静之节。已属过时之闻。而尔来瞻仰之积。复已多时。谨未审徂玆春殷。联床道体对序休泰否。岱镇亲年益高。惧多于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29L 页
 喜。兼改岁以后屡经外感。迄少安日。旁状遣免未足自幸。所事佔毕。因循放过。顾省胸中。草木日塞。似此悠悠。终何底止。每引领门墙。思与二三子从容其间。时蒙提撕警发之益。而坐在里许。辄有欲从末由之叹。恐遂虚了一生而止耳。柰何柰何。体用说蒙赐印许。自今谨当笃信而不易矣。程子一原之义。固专指形而上者言之。然就此形上处分体用。则形上者即其体。而发见于形下者为之用。故朱子释此一段。有曰自理而言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故曰一原。其曰自理而言者。固以这体用专做形上说。而其曰理体象用者。却兼就形上下分合说矣。然此岂直以无形之理为体而有形之器为用哉。亦曰形上者为体而发见于形下者为之用云耳。前书所谓就形上下分合说者。意正如此。来诲以其直谓形上为体形下为用而烦赐斤正。此则言语未莹之致。而其意则不至如是之舛戾也。至谓体用有心与理之别者。固若差谬。然言理则即体而用具。是所谓有则俱有也。言心则体发而为用。自当以时处分也。且未知语心之体用而下个一原字则果为稳帖乎。就令下得。
喜。兼改岁以后屡经外感。迄少安日。旁状遣免未足自幸。所事佔毕。因循放过。顾省胸中。草木日塞。似此悠悠。终何底止。每引领门墙。思与二三子从容其间。时蒙提撕警发之益。而坐在里许。辄有欲从末由之叹。恐遂虚了一生而止耳。柰何柰何。体用说蒙赐印许。自今谨当笃信而不易矣。程子一原之义。固专指形而上者言之。然就此形上处分体用。则形上者即其体。而发见于形下者为之用。故朱子释此一段。有曰自理而言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故曰一原。其曰自理而言者。固以这体用专做形上说。而其曰理体象用者。却兼就形上下分合说矣。然此岂直以无形之理为体而有形之器为用哉。亦曰形上者为体而发见于形下者为之用云耳。前书所谓就形上下分合说者。意正如此。来诲以其直谓形上为体形下为用而烦赐斤正。此则言语未莹之致。而其意则不至如是之舛戾也。至谓体用有心与理之别者。固若差谬。然言理则即体而用具。是所谓有则俱有也。言心则体发而为用。自当以时处分也。且未知语心之体用而下个一原字则果为稳帖乎。就令下得。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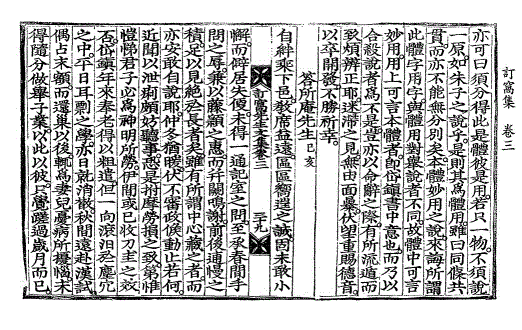 亦可曰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若只一物。不须说一原。如朱子之说乎。是则其为体用。虽曰同条共贯。而亦不能无分别矣。本体妙用之说。来诲所谓此体字用字。与体用对举说者不同。故体中可言妙用。用上可言本体者。即岱镇书中意也。而乃以合杀说者为不是。岂亦以命辞之际。有所流遁而致烦辨正耶。迷滞之见。无由面㬥。伏望重赐德音。以卒开发。不胜祈幸。
亦可曰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若只一物。不须说一原。如朱子之说乎。是则其为体用。虽曰同条共贯。而亦不能无分别矣。本体妙用之说。来诲所谓此体字用字。与体用对举说者不同。故体中可言妙用。用上可言本体者。即岱镇书中意也。而乃以合杀说者为不是。岂亦以命辞之际。有所流遁而致烦辨正耶。迷滞之见。无由面㬥。伏望重赐德音。以卒开发。不胜祈幸。答所庵先生(己亥)
自绊乘下邑。教席益远。区区向𨓏之诚。固未敢小懈。而僻居失便。未得一通记室之问。至承春间手问之辱。兼以藤颖之惠。而并阙鸣谢。前后逋慢之积。足以见绝于长者矣。虽有所谓中心藏之者。而亦安敢自说耶。仲冬犹暖。伏不审政候动止若何。近闻以泄痢颇妨听事。恐是拊摩劳损之致。第惟恺悌君子必为神明所劳。伊间或已收刀圭之效否。岱镇年来奉老得以粗遣。但一向滚汩于尘冗之中。平日耳剽之学。亦日就消散。秋间远赴汉试。偶占末额。而还巢以后。辄为妻儿忧病所扰恼。未得随分做举子业。以此以彼。只觉蹉过岁月而已。
订窝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30L 页
 似此悠悠。何足仰闻于眷念之下哉。仄闻视郡以来。阖境颇苏息。存心爱物。此其验矣。外此而一行气力复有及于著书立言之业者耶。此实所愿闻也。岱镇周旋函丈。前此已无几。而今复落落以远。临风驰义。第有怅黯政远。惟祝为民保重。以副区区。
似此悠悠。何足仰闻于眷念之下哉。仄闻视郡以来。阖境颇苏息。存心爱物。此其验矣。外此而一行气力复有及于著书立言之业者耶。此实所愿闻也。岱镇周旋函丈。前此已无几。而今复落落以远。临风驰义。第有怅黯政远。惟祝为民保重。以副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