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进奄(一作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杂著
杂著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3H 页
 严光论
严光论严光。光武之故人也。少同游学。及帝即位。被羊裘钓泽中。若与帝无一面之雅。至以物色求之。然后始乃一至洛阳。不肯受谏议。退老于富春山中。乐耕钓以终。光武亦不能屈其志。其所以激顽起懦扶植风化之美者。秦汉间一人而已矣。而顾以菅蒯一匹夫。接万乘之尊。卧而不起。睡而不应。加足帝腹。非严光则不可能。非光武则不能容。岂不盛哉。然而考其迹度其义。谓之山林高士则可。谓之中行君子则不可也。何也。前日则南阳一故旧也。无所踰等。而今日则君臣之分已定矣。以光武言之。待以不臣之礼。诚明主圣君之事。而以子陵言之。乌可以不君其君乎。不以宾师之礼。则爵禄可辞也。必遂高尚之志。则王侯不事也。惟卧而不起不可。眠而不应不可也。况以蹇贱之足。加于至尊之腹哉。光武之容受。实有三代帝王尚贤厚礼底气象。而于子陵臣子之分。不几近于骄傲而过高乎。心常起疑而未能融释矣。近见朱子纲目。言不屈事甚悉。而略不及不起不应加足等事。张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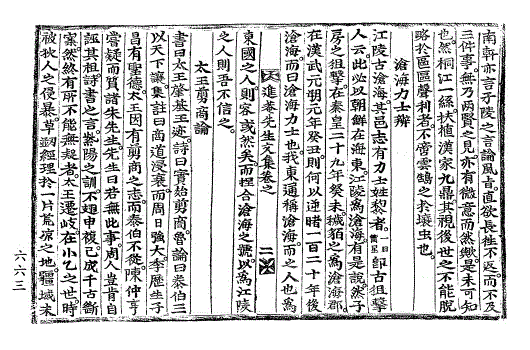 南轩亦言子陵之言论风旨。直欲长往不返。而不及三件事。无乃两贤之见。亦有微意而然欤。是未可知也。然桐江一丝。扶植汉家九鼎。其视后世之不能脱略于区区声利者。不啻云鹄之于壤虫也。
南轩亦言子陵之言论风旨。直欲长往不返。而不及三件事。无乃两贤之见。亦有微意而然欤。是未可知也。然桐江一丝。扶植汉家九鼎。其视后世之不能脱略于区区声利者。不啻云鹄之于壤虫也。沧海力士辨
江陵古沧海。其邑志有力士姓黎者(一曰冲星)。即古狙击人云。此必以朝鲜在海东。江陵为沧海。有是说。然子房之狙击。在秦皇二十九年癸未。秽貊之为沧海郡。在汉武元朔元年癸丑。则何以逆睹一百二十年后沧海。而曰沧海力士也。我东通称沧海。而之人也为东国之人。则容或然矣。而捏合沧海之号。以为江陵之人则吾不信之。
太王剪商论
书曰太王肇基王迹。诗曰实始剪商。鲁论曰泰伯三以天下让。集注曰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生子昌有圣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从。陈仲亨尝疑而质诸朱先生。先生曰若无此事。周人岂肯自诬其祖。诗书之言。紫阳之训。不翅申复。已成千古断案。然终有所不能无疑者。太王迁岐。在小乙之世。时被狄人之侵暴。草刱经理于一片荒凉之地。疆域未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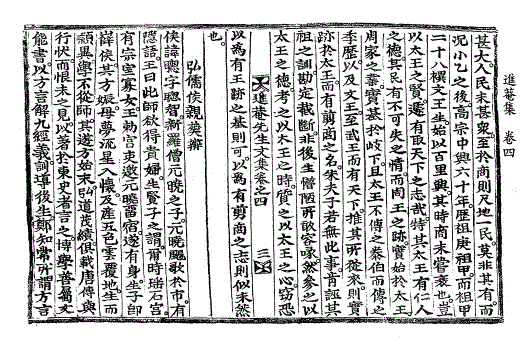 甚大。人民未甚众。至于商则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况小乙之后。高宗中兴六十年。历祖庚祖甲。而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始以百里兴。其时商未尝衰也。岂以太王之贤。遽有取天下之志哉。特其太王有仁人之德。其民有不可失之情。而周王之迹。实始于太王。周家之业。实基于岐下。且太王不传之泰伯而传之季历。以及文王。至武王而有天下。推其所从来。则实迹于太王。而有剪商之名。朱夫子若无此事。肯诬其祖之训。勘定截断。非后生懵陋所敢容喙。然参之以太王之德。考之以太王之时。质之以太王之心。窃恐以为有王迹之基则可。以为有剪商之志则似未然也。
甚大。人民未甚众。至于商则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况小乙之后。高宗中兴六十年。历祖庚祖甲。而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始以百里兴。其时商未尝衰也。岂以太王之贤。遽有取天下之志哉。特其太王有仁人之德。其民有不可失之情。而周王之迹。实始于太王。周家之业。实基于岐下。且太王不传之泰伯而传之季历。以及文王。至武王而有天下。推其所从来。则实迹于太王。而有剪商之名。朱夫子若无此事。肯诬其祖之训。勘定截断。非后生懵陋所敢容喙。然参之以太王之德。考之以太王之时。质之以太王之心。窃恐以为有王迹之基则可。以为有剪商之志则似未然也。弘儒侯亲葬辨
侯讳聪字聪智。新罗僧元晓之子。元晓飏歌于市。有隐语。王曰此师欲得贵妇。生贤子之谓。尔时瑶石宫。有宗室寡女。王敕宫吏邀元晓留宿。遂有身。生子即嶭(一作薛)侯。其方娠。母梦流星入怀。及产五色云覆地。生而颖异。学不从师。其游方始末。弘道茂绩。俱载唐传与行状。而恨未之见。以著于东史者言之。博学善属文能书。以方言解九经义。训导后生。郑知常所谓方言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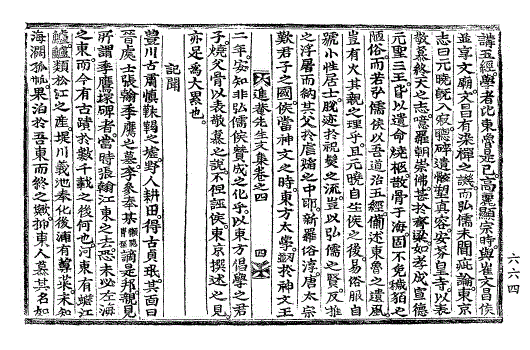 讲五经。学者比东鲁是已。高丽显宗时。与崔文昌侯并享文庙。文昌有染禅之讥。而弘儒未闻疵论。东京志曰元晓既入寂。聪碎遗骸塑真容。安芬皇寺。以表敬慕终天之志。噫罗朝崇佛。甚于齐梁。如孝成宣德元圣三王。皆以遗命烧柩。散骨于海。固不免秽貊之陋俗。而若弘儒侯以吾道治五经。备述东鲁之遗风。岂有火其亲之理乎。且元晓自生侯之后。易俗服自号小性居士。脱迹于祝发之流。岂以弘儒之贤。反推之浮屠而纳其父于虐焰之中耶。新罗俗淳。唐太宗叹君子之国。侯当神文之时。东方太学。刱于神文王二年。安知非弘儒侯赞成之化乎。以东方倡学之君子。烧父骨以表敬慕之说。不但诬侯。东京撰述之见。亦足为大累也。
讲五经。学者比东鲁是已。高丽显宗时。与崔文昌侯并享文庙。文昌有染禅之讥。而弘儒未闻疵论。东京志曰元晓既入寂。聪碎遗骸塑真容。安芬皇寺。以表敬慕终天之志。噫罗朝崇佛。甚于齐梁。如孝成宣德元圣三王。皆以遗命烧柩。散骨于海。固不免秽貊之陋俗。而若弘儒侯以吾道治五经。备述东鲁之遗风。岂有火其亲之理乎。且元晓自生侯之后。易俗服自号小性居士。脱迹于祝发之流。岂以弘儒之贤。反推之浮屠而纳其父于虐焰之中耶。新罗俗淳。唐太宗叹君子之国。侯当神文之时。东方太学。刱于神文王二年。安知非弘儒侯赞成之化乎。以东方倡学之君子。烧父骨以表敬慕之说。不但诬侯。东京撰述之见。亦足为大累也。记闻
礼川古肃慎靺鞨之墟。野人耕田。得古贞珉。其面曰晋处士张翰季鹰之墓。李参奉某(懒隐胄孙)谪是邦。亲见所谓季鹰冢碑者。当时张翰江东之去。恐未必左海之东。而今有古迹于数千载之后何也。河东有蟾江鲈。鲈类松江之产。堤川义池奉化后浦有莼菜。未知海𤄃孤帆。果泊于吾东而终之欤。抑东人慕其名如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5H 页
 郦食其审食其之效司马食其者。然姓张者同其名同其字欤。然而晋处士三字。无所归宿。姑记所闻。以俟博识之勘正云尔。
郦食其审食其之效司马食其者。然姓张者同其名同其字欤。然而晋处士三字。无所归宿。姑记所闻。以俟博识之勘正云尔。名利相让
寄轩姜公讳楷。其兄子曰必龟。文科知中枢也。中枢之母夫人。韩山李玄年女。当庭试。以方席一坐。推之寄轩曰梦龙蟠此座。登第必矣。公让之曰嫂之子方应试。何以让我。嫂曰叔叔父也。儿从子也。义当叔先。固予之。中枢实未闻其梦也。见叔座三重。请其一。公举尻而使自择焉。公拔其所梦之座而果登第。噫母不予子而予叔。大义也。叔不自为操纵而使侄拔之。听天理也。嫂叔处义。两皆巍磊。而寄轩知道之君子。固不以名利动其心。李氏以闺中一妇人。知大阐之兆而不私其子。尤岂不卓荦矣乎。让之叔而卒归其子。得失皆命也。亦可验天理之公行。而食报之说。果不诬也。
书示举子
传曰赵孟之所贵。赵孟贱之。当时之人之贵之贱。一出赵孟之手。则若可力求于赵孟。而赵孟亦有不能容力者存何也。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坡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5L 页
 缄一简送方叔。时方叔不在。章惇二子曰持曰援者适到其家。窃视之。乃杨雄优于刘向论一编。二章喜而窃去。及坼号。坡意魁必方叔。乃章援也。第十名文义。与魁相似者。坼之又章持也。坡失色。乃择其一券颇奇者。以示同列曰。此必李方叔。及坼乃葛敏修也。坡即其时赵孟。而三坼三误。其得失岂非命乎。淳熙中。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有布衣交屡屈礼部者。以书约会于富阳萧寺。更深附耳语曰某此行与贡举。省试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为验。玉山既知举。搜诸券。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及坼非友人也。私窃怪之。后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泄之。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问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默然良久对曰玆事甚怪。某之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与僧步庑下。见室中有棺。僧曰此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杳无骨肉来矣。是夕梦一女子来诿曰试券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勿相忘。使妾朽骨得入土。遂用其言果验矣。玉山亦其时赵孟。而其友失之。他人横取。则亦岂非命乎。余于乙未赴东堂会试。时李光文为二所试官。其子赴一所。呈
缄一简送方叔。时方叔不在。章惇二子曰持曰援者适到其家。窃视之。乃杨雄优于刘向论一编。二章喜而窃去。及坼号。坡意魁必方叔。乃章援也。第十名文义。与魁相似者。坼之又章持也。坡失色。乃择其一券颇奇者。以示同列曰。此必李方叔。及坼乃葛敏修也。坡即其时赵孟。而三坼三误。其得失岂非命乎。淳熙中。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有布衣交屡屈礼部者。以书约会于富阳萧寺。更深附耳语曰某此行与贡举。省试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为验。玉山既知举。搜诸券。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及坼非友人也。私窃怪之。后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泄之。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问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默然良久对曰玆事甚怪。某之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与僧步庑下。见室中有棺。僧曰此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杳无骨肉来矣。是夕梦一女子来诿曰试券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勿相忘。使妾朽骨得入土。遂用其言果验矣。玉山亦其时赵孟。而其友失之。他人横取。则亦岂非命乎。余于乙未赴东堂会试。时李光文为二所试官。其子赴一所。呈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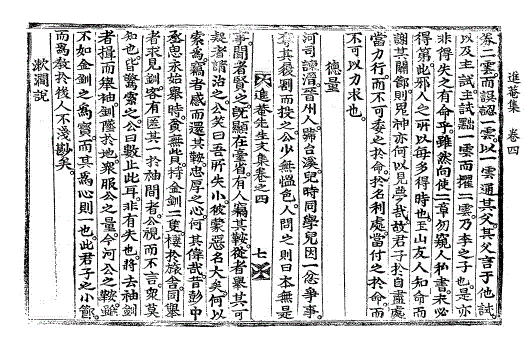 券二云。而误认一云。以一云通其父。其父言于他试。以及主试。主试黜一云而擢二云。乃李之子也。是亦非得失之有命乎。虽然向使二章勿窥人私书。未必得第。此邪人之所以每多得时也。玉山友人知命而谢其关节。则鬼神亦何以见梦哉。故君子于自尽处当力行。而不可委之于命。于名利处。当付之于命。而不可以力求也。
券二云。而误认一云。以一云通其父。其父言于他试。以及主试。主试黜一云而擢二云。乃李之子也。是亦非得失之有命乎。虽然向使二章勿窥人私书。未必得第。此邪人之所以每多得时也。玉山友人知命而谢其关节。则鬼神亦何以见梦哉。故君子于自尽处当力行。而不可委之于命。于名利处。当付之于命。而不可以力求也。德量
河司谏溍。晋州人。号台溪。儿时同学儿因一忿争事。夺其履割而投之。公少无愠色。人问之则曰本无是事。闻者贤之。既显在台省。有人窃其鞍。从者举其可疑者请治之。公笑曰吾所失小。彼蒙恶名大矣。何以索为。窃者感而还其鞍。忠厚之心。何其伟哉。昔彭中丞思永始举时。贫无赀。持金钏二只。栖于旅舍。同举者求见钏。客有匿其一于袖间者。公视而不言。众莫知也。皆惊索之。公曰数止此耳。非有失也。将去袖钏者揖而举袖。钏坠于地。众服公之量。今河公之鞍。虽不如金钏之为宝。而其为心则一也。此君子之小节。而为教于后人不浅鲜矣。
漱涧说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6L 页
 吴临川自新铭曰。齿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积。又曰本白而我自污。谁之辜。幸而一朝漱其齿。白者复尔。盖不漱则污。漱则复其所以自新者。岂真在漱齿而已哉。许友静守自少喜漱口。颒必漱。食已必漱。漱至日四三而不自已焉。故从者进沃与进膳。辄备漱具以待。其于日新之工。为何如哉。因而自号曰漱涧。涧水之洁者也。翁居江海之滨。貌礼而晢。口止而讷。隐而不衒。施而好德。揭厉以自适。视世之脆其颜蜜其口而污心秽德。颠冥黝垩者。不啻雪月之皎冰檗之洁矣。然欲漱口。当先漱心。欲漱心。必先漱德。心必洗之而致其精。德必浴之而克其明。然后睟于面盎于背。畅于四肢。无有一毫疵累于子之身矣。
吴临川自新铭曰。齿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积。又曰本白而我自污。谁之辜。幸而一朝漱其齿。白者复尔。盖不漱则污。漱则复其所以自新者。岂真在漱齿而已哉。许友静守自少喜漱口。颒必漱。食已必漱。漱至日四三而不自已焉。故从者进沃与进膳。辄备漱具以待。其于日新之工。为何如哉。因而自号曰漱涧。涧水之洁者也。翁居江海之滨。貌礼而晢。口止而讷。隐而不衒。施而好德。揭厉以自适。视世之脆其颜蜜其口而污心秽德。颠冥黝垩者。不啻雪月之皎冰檗之洁矣。然欲漱口。当先漱心。欲漱心。必先漱德。心必洗之而致其精。德必浴之而克其明。然后睟于面盎于背。畅于四肢。无有一毫疵累于子之身矣。文石说
京兆右尹朴公光锡。尝语余曰吾尝奉 命诣奎章阁。有蓝浦梅花石。大如叩饼木板。其状如古查梅奇崛。花之蓓蕾者半开者已开者。天然精妙。其上有青红双雀。交喙而若戏。吾尝守蓝浦。多见文石之奇。而未见知是石之神妙。石在水中。未尝经人之手巧而能如许。天地造化之理。不可得以窥测矣。余闻其说而不能格其理。尝见眉叟书。有熊渊文石记。渊在长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7H 页
 景下十五里涟西之地。乱后石文出。石青字黑。或竖或横或合或散。类龙蛇草木形。而怪诡不可形状。有一邑宰剥得数字而去。剥深二寸。石文亦二寸。盖鬼神之文。权永文曰石文与石俱生不可知。或气化成之。其言得之矣。读之恍然若有悟。盖天之日月星辰之文。地之山川草木鸟兽之文。皆人所恒见。故不以为奇。至于骊图龟书卿云嘉禾之文。人所罕见者。而必以为瑞。然则化工之妙著于物。一出于理。而或常或变或显或幽。亦不可以二之也。
景下十五里涟西之地。乱后石文出。石青字黑。或竖或横或合或散。类龙蛇草木形。而怪诡不可形状。有一邑宰剥得数字而去。剥深二寸。石文亦二寸。盖鬼神之文。权永文曰石文与石俱生不可知。或气化成之。其言得之矣。读之恍然若有悟。盖天之日月星辰之文。地之山川草木鸟兽之文。皆人所恒见。故不以为奇。至于骊图龟书卿云嘉禾之文。人所罕见者。而必以为瑞。然则化工之妙著于物。一出于理。而或常或变或显或幽。亦不可以二之也。玉水事
日本处士玉水。抄退陶集编为十卷。命之曰退溪书抄。文化三年丙寅。佐嘉古贺朴序之。六年己巳。寒泉冈田恕识之。其编次类例。未之得见。而就考识文。则曰犹退溪氏有朱书节要之作也。其序文则深斥王伯安之诋朱子之学。尊信老先生之得朱子之心。噫日本在东海中本黑齿。周幽王时神武天皇始立国。自谓泰伯之后。秦始皇时方士徐韨入海。为黑齿别种。齐梁时山城主允恭始称姓。为藤氏平氏源氏橘氏。其俗信鬼神事浮屠好清净。以跣足赤顶。膝行匍匐为恭。无拜礼。性淫巧尚奇技。与南蛮通。轻信易怒。好击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7L 页
 刺。玉水子出于其中。扶正道辟异说。尊朱子退陶之学。表章之依归之。岂非豪杰之士乎。其氏村上名宗章字幸藏。玉水其号也。其先仕于大和筒井氏。筒井氏亡。移居江户。诸侯闻其名。多厚礼以聘之。皆辞不就。以处士终云。
刺。玉水子出于其中。扶正道辟异说。尊朱子退陶之学。表章之依归之。岂非豪杰之士乎。其氏村上名宗章字幸藏。玉水其号也。其先仕于大和筒井氏。筒井氏亡。移居江户。诸侯闻其名。多厚礼以聘之。皆辞不就。以处士终云。文者贯道之器论
有道者必有文。有文者未必有道。则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何能为贯道之器哉。朱夫子曰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而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道自道。而紫阳所谓他大病处是已。盖文自史皇造字之后。不可一日无有。礼乐教化之政。典章仪物之数。尧舜授受之道。孔孟继开之功。无不包括于文。而不有多识之工。则虽欲造道之极处。无异冥行擿埴。而求道于盲也。乌可以履如砥之道而建极于荡荡平平之域哉。惟其然也。故韩文公特其因文悟道。而未能深造本原。只得扶起衰文。与李汉之序曰文者贯道之器。乌得免回头错应人之讥乎。文公终是不明于道。役心于文。故原道曰博爱之谓仁。原性曰性有三品。先伩所以目之以无头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8H 页
 之学。全没格致之工者。专由于以文贯道之致也。苟能真积力久。入道而蹊遥不迷。行道而造履坦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则经天纬地之文。素经底麟之文。闇然日章于道体之滋润。而根本植立。枝叶畅敷矣。肆昔陈才卿读韩文至此。求教于朱先生。先生曰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只如吃饭时下饭。且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墧于是知文不可以贯道也。
之学。全没格致之工者。专由于以文贯道之致也。苟能真积力久。入道而蹊遥不迷。行道而造履坦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则经天纬地之文。素经底麟之文。闇然日章于道体之滋润。而根本植立。枝叶畅敷矣。肆昔陈才卿读韩文至此。求教于朱先生。先生曰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只如吃饭时下饭。且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墧于是知文不可以贯道也。桧渊书院讲义
中庸
李种烨问。喜怒哀乐未发。何以谓之中。讲长答曰。未发之前。混然天理。无所偏倚。方是恰好处。故曰中。
李时钦讲篇题问。退藏于密之密字何义。答曰程子曰密者用之源。圣人之妙处。朱子曰密者静也。参互两说。程说尤有味。又问不偏不倚何别。曰偏是偏颇之意。倚是倚著一处。子路问强章句曰倚偏著也。唯天下至诚章句曰夫岂有所倚著于物。观一著字。旨义自别。又问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正与定。有异义欤。答曰正。大中至正之谓。定。一定不易之义。又问心一也而有未发之中。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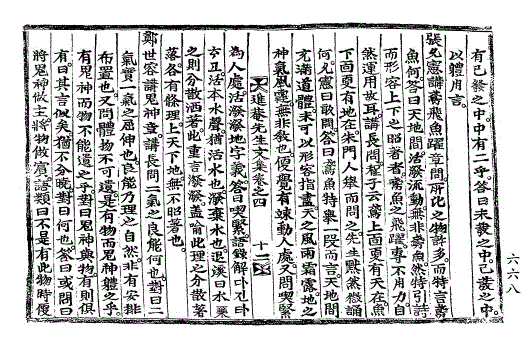 有已发之中。中有二乎。答曰未发之中。已发之中。以体用言。
有已发之中。中有二乎。答曰未发之中。已发之中。以体用言。张允宪讲鸢飞鱼跃章问。所比之物许多。而特言鸢鱼何。答曰天地间。活泼流动。无非鸢鱼。然特引诗而形容上下之昭著者。鸢鱼之飞跃。专不用力。自然运用故耳。讲长问。程子云鸢上面更有天在。鱼下面更有地在。朱门人举而问之。先生默然微诵何。允宪曰敢问。答曰鸢鱼特举一段而言。天地间充满道体。未可以形容指尽。天之风雨霜露。地之神气风霆。无非教也。便觉有竦动人处。又问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字义。答曰吃紧。语录解다긴타고。活本水声。犹活水也。泼弃水也。退溪曰水弃之则分散洒著。此重言泼泼。盖喻此理之分散著落。各有条理。上天下地。无不昭著也。
郑世容讲鬼神章。讲长问二气之良能何也。对曰二气实一气之屈伸也。良能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也。又问体物不可遗。是有物而鬼神体之乎。有鬼神而物不能遗之乎。对曰鬼神与物。有则俱有。曰其言似矣。犹不分晓。对曰何也。答曰或问曰将鬼神做主。将物做宾。语类曰不是有此物时便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9H 页
 有此鬼神。有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违乎鬼神。观此数说。可详其鬼神为物之主。有这鬼神了。方有此物。而物不能遗其体干也。又问天地之鬼神。庙享之鬼神同乎。答曰末言庙享之鬼神。举亲切而言。非有异也。又问鬼神理乎气乎。答曰无无理之气。又无无气之理。然各有立言之不同。专言鬼神则气也。曰鬼神之德。曰良能曰性情。兼言理也。又问体物。犹易所谓干事何。答曰干事。语类以主宰言。
有此鬼神。有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违乎鬼神。观此数说。可详其鬼神为物之主。有这鬼神了。方有此物。而物不能遗其体干也。又问天地之鬼神。庙享之鬼神同乎。答曰末言庙享之鬼神。举亲切而言。非有异也。又问鬼神理乎气乎。答曰无无理之气。又无无气之理。然各有立言之不同。专言鬼神则气也。曰鬼神之德。曰良能曰性情。兼言理也。又问体物。犹易所谓干事何。答曰干事。语类以主宰言。郑基和讲博厚所以载物章。讲长问博厚配地仁也。高明配天知也。仁先知后何。对曰以入德言则知先仁后。以成德言则仁先知后。又问章首无息不息似有别。游杨之说恐然矣。而朱子以为未然何。基和请问其义。答曰不息则久以下。便是工夫煞高。又岂有别般无息地位耶。故朱子曰不息。只如言无息。
文定洛讲唯天下至诚章。讲长问编内两言唯天下至诚。而结语。一曰赞化育。一曰知化育。赞与知有别否。对曰赞化育以行言。知化育以知言。有浅深之别。曰不然。尽其性者。从里而说出去。故尽其性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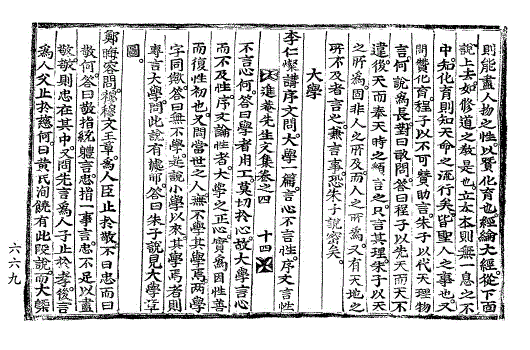 则能尽人物之性。以赞化育也。经纶大经。从下面说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大本则无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则知天命之流行矣。皆圣人之事也。又问赞化育。程子以不可赞助言。朱子以代天理物言。何说为长。对曰敢问。答曰程子以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之类言之。只言其理。朱子以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言之。兼言事。恐朱子说密矣。
则能尽人物之性。以赞化育也。经纶大经。从下面说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立大本则无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则知天命之流行矣。皆圣人之事也。又问赞化育。程子以不可赞助言。朱子以代天理物言。何说为长。对曰敢问。答曰程子以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之类言之。只言其理。朱子以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言之。兼言事。恐朱子说密矣。大学
李仁灿讲序文问。大学一篇。言心不言性。序文言性不言心何。答曰学者用工。莫切于心。故大学言心而不及性。序文论性者。大学之正心。实为因性善而复性初也。又问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两学字同欤。答曰无不学。是说小学以来。其学焉者则专言大学。问此说有据耶。答曰朱子说见大学章图。
郑晦容问。穆穆文王章。为人臣止于敬。不曰忠而曰敬何。答曰敬指统体言。忠指一事言。忠不足以尽敬。敬则忠在其中。又问先言为人子止于孝。后言为人父止于慈何。曰黄氏洵饶有此段说。而大槩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0H 页
 以孝慈难易。为先后说。然恐非本文正义。大凡为人子而后可以为人父。孝于亲而后可以慈于子。
以孝慈难易。为先后说。然恐非本文正义。大凡为人子而后可以为人父。孝于亲而后可以慈于子。金振泰讲传十章。至君子有大道。问章句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何。答曰始言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以人言者。中言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以己言者。终言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以心言者。
许休讲一家仁章。问仁以一家言。让以一国言。仁让之化。若是其难。而末段曰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贪戾之祸。如彼其甚何。答曰有陈氏许氏诸说。盖为善难为恶易。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不可忽如此。
郑命和讲经一章。问明德。答曰语类或以五伦言之。或以四端言之。明儒张叔舆曰明德者。心之本体。孟子所谓本心良心是也。然德者心之所得至善之理。人之得于天则明命也。以属火之心体。有虚灵不昧之质。明德之必以心言之者是。而章句所谓具众理性也。应万事情也。统得心性情之所当然所以然。而光明正大。无所亏欠。乃是明德。
丹山书堂讲义
小学(直日。张龙焕,李观熙,宋寅璧。)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0L 页
 李承熙读元亨利贞章。问性有四纲欤。分言则四者为万善之纲。统言则性为四者之纲。而奚独以四者为性之纲欤。答曰性之所以为性。以有四德也。以四德为万善之纲则可。以性为四德之纲则不可。讲长问。性是未发之全体。而未有四德之界分。则何以知有仁义礼智。而撰出四德之名目。对曰因其发而知之乎。曰然。
李承熙读元亨利贞章。问性有四纲欤。分言则四者为万善之纲。统言则性为四者之纲。而奚独以四者为性之纲欤。答曰性之所以为性。以有四德也。以四德为万善之纲则可。以性为四德之纲则不可。讲长问。性是未发之全体。而未有四德之界分。则何以知有仁义礼智。而撰出四德之名目。对曰因其发而知之乎。曰然。吕轸奎读颜渊克己复礼章。讲长问视箴言心。听箴言性。对曰视属心。听属性欤。曰此说含胡。由中而应外者心为主。开眼而接物者视为先。故视箴必言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诐淫之辞。诱于外而凿其性。故听箴必言性也。
郑匡锡读箕子亲戚章。问或谓微子之去。欲存宗祀。箕子之不死。以存皇极之法。其说然否。答曰武庚诛而立微子。武王问而陈洪范。此后来适然耳。谓之预必而如是云则未莹彻。此胡五峰之说所以见非于延平先生也。又问箕子朝周之说是否。答曰箕子渡浿。实有罔仆之志也。若复朝于周。则是仆于武王。箕子必无是理。
张奎斌读胡文定公与子书。问明道希文门路有异。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1H 页
 而并言立志何。答曰士君子为学。必先立其志。然后可以做将去。而耳目之所逮。莫如程明道之存心爱物。范文定之先忧后乐。故特于立志处并言。
而并言立志何。答曰士君子为学。必先立其志。然后可以做将去。而耳目之所逮。莫如程明道之存心爱物。范文定之先忧后乐。故特于立志处并言。李锡弼读贤贤易色章。讲长问程子言改容易色。朱子言如好好色。二说何从。对曰朱子非不知程子之言。而为此说。则可见诚心好贤之意精切。
郑载锡读三十而有室章。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何。答曰此是参天两地。倚数以象天地。周礼有此说。又读张公艺九世同居章。问九世之久。古今无复有如此者。而忍字之外。不复有别般道乎。答曰皇明郑湜十世同居。自上问其道。湜曰不听妇人言为家法。此说甚善。
宋礼翼读孟子道性善章。问孟子云性善。而明道云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何。答曰性一也。而所指者不同。就本源禀受而言。则天命纯粹。有善无恶。此孟子所谓性善。就堕在气质言。则气禀万殊。或善或恶。此张子所谓气质之性。
李九相读贤哉回也章。讲长问贫亦可乐乎。对曰非乐其贫。自有其乐也。讲长曰此乐字。周子亦引而不发。未敢妄言。然安贫乐道之说。邹氏非之。恐乐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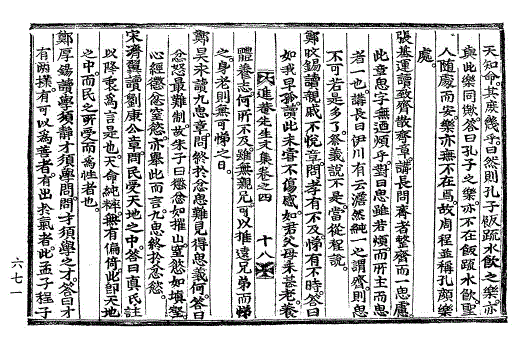 天知命。其庶几乎。曰然则孔子饭疏水饮之乐。亦与此乐同欤。答曰孔子之乐。亦不在饭疏水饮。圣人随处而安。乐亦无不在焉。故周程并称孔颜乐处。
天知命。其庶几乎。曰然则孔子饭疏水饮之乐。亦与此乐同欤。答曰孔子之乐。亦不在饭疏水饮。圣人随处而安。乐亦无不在焉。故周程并称孔颜乐处。张基运读致齐散齐章。讲长问齐者整齐而一思虑。此章思字无乃烦乎。对曰思虽若烦。而所主而思者一也。讲长曰伊川有云澹然纯一之谓齐。则思不可若是多了。祭义说不是。当从程说。
郑旼锡读亲戚不悦章。问孝有不及。悌有不时。答曰如我早孤。读此未尝不伤感。如君父母未甚老。养体养志。何所不及。虽无亲兄。可以推远兄弟而悌之。身老则无可悌之日。
郑昊永读九思章。问终于忿思难见得思义何。答曰忿怒最难制。故朱子曰惩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心经惩忿窒欲。亦举此而言。九思终于忿欲。
宋济翼读刘康公章。问民受天地之中。答曰真氏注以降衷为言是也。天命纯粹。无有偏倚。此即天地之中。而民之所受而为性者也。
郑厚锡读学须静才须学问。问才须学之才。答曰才有两㨾。有可以为善者。有出于气者。此孟子程子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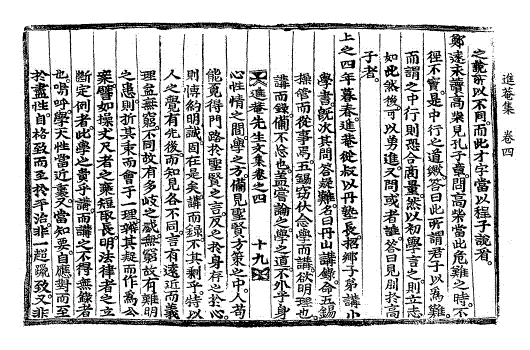 之说所以不同。而此才字当以程子说看。
之说所以不同。而此才字当以程子说看。郑远永读高柴见孔子章。问高柴当此危难之时。不径不窦。是中行之道欤。答曰此所谓君子以为难。而谓之中行则恐合商量。然以初学言之。则立志如此然后。可以勇进。又问或者谁。答曰见刖于高子者。
上之四年暮春。进庵从叔以丹塾长。招乡子弟讲小学书。既次其问答疑难。名曰丹山讲录。命五锡操管而从事焉。五锡窃伏念学而讲。欲明理也。讲而录。备不忘也。盖尝论之。学之道。不外乎身心性情之间。学之方。备见圣贤方策之中。人苟能觅得门路于圣贤之言。反之于身存之于心。则博约明诚。固在是矣。讲而录。不其剩乎。特以人之觉有先后。而知见各不同。言有远近而义理益无穷。不同故有多岐之惑。无穷故有难明之患。则折其𣏮而会于一理。辨其疑而作为公案。譬如操丈尺者之弃短取长。明法律者之立断定例者。此学之贵乎讲。而讲之不得无录者也。呜呼。学天性当近里。又当知要。自应对而至于尽性。自格致而至于平治。非一超躐致。又非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2L 页
 一毫可外求者。则彼世之不知洒扫。而驰心高远之域。出入四寸。而要为标帜之资者。岂今日公之所以必讲小学而作为是录之意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朱夫子曰为小学者。不由乎敬。无以谨夫洒扫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从事于斯。以立基本。则庶几不负是录之意。而若其尽心知性。驯致乎约且诚焉而达天德。则亦岂尽以言说求哉。学者要躬行默识。引类而广之耳。可不勉哉。役既讫。敬书于尾以献。丁卯三月下浣。再从侄五锡谨识。
一毫可外求者。则彼世之不知洒扫。而驰心高远之域。出入四寸。而要为标帜之资者。岂今日公之所以必讲小学而作为是录之意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朱夫子曰为小学者。不由乎敬。无以谨夫洒扫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从事于斯。以立基本。则庶几不负是录之意。而若其尽心知性。驯致乎约且诚焉而达天德。则亦岂尽以言说求哉。学者要躬行默识。引类而广之耳。可不勉哉。役既讫。敬书于尾以献。丁卯三月下浣。再从侄五锡谨识。论语(戊辰二月。直日金台应,宋寅濩。参讲李震相,郑五锡。)
金台应读颜渊问仁章。讲长问克己复礼则便是仁否。抑为仁有差别欤。对曰克己复礼便是仁。恐不可以工夫次第言。讲长曰不然。克己复礼。已至十分精到。则谓之仁可矣。而方做克己复礼之工。则何可便谓之仁乎。故必著为字于仁字之上。且其释不曰仁되오미而仁요미则为字有深意。胡氏曰非礼勿视。非是仁。真积力久。自然诚实。则可谓之仁亦可见矣。又问这礼字即是理。不曰理而曰礼何。对曰理字虚而无形影。礼字实而有准则。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3H 页
 所以曰礼也。李震相问一日之内。天下便归仁否。答曰仁之理。天下之人皆同。近者归仁则远者亦可知。此言理当如此。非一日之内。天下便归仁也。台应问性偏难克处克将去。用工何以则可。答曰刚者每失于褊急。此刚之偏也。柔者每失于惰缓。此柔之偏也。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乃是克将去道理。而此甚难。故曰难克处。欲变化气质。先难而后获。李震相曰非礼者。己之私也。此非礼字。是自外至者欤。抑己心中之非礼者欤。答曰非礼有自外至底。勿视勿听是也。有自内出底。勿言勿动是也。李震相曰己心之涉于非礼者是也。虽属外物。而自是己事也。答曰此未可以言内而不言外。亦未可以言外而不言内。有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者。岂不以自外至者言之乎。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所以养其外。淫乐慝礼。不接心𧗱。所以养其内。兼内外说得备。台应问何以曰久而诚。答曰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久久积功。然后可以言诚。诚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斯可谓之仁。岂略绰可做底乎。郑五锡问知诱物化。何独言于听箴。李震相曰感于物而动。惟在于听。故独于听箴言之。讲长曰
所以曰礼也。李震相问一日之内。天下便归仁否。答曰仁之理。天下之人皆同。近者归仁则远者亦可知。此言理当如此。非一日之内。天下便归仁也。台应问性偏难克处克将去。用工何以则可。答曰刚者每失于褊急。此刚之偏也。柔者每失于惰缓。此柔之偏也。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乃是克将去道理。而此甚难。故曰难克处。欲变化气质。先难而后获。李震相曰非礼者。己之私也。此非礼字。是自外至者欤。抑己心中之非礼者欤。答曰非礼有自外至底。勿视勿听是也。有自内出底。勿言勿动是也。李震相曰己心之涉于非礼者是也。虽属外物。而自是己事也。答曰此未可以言内而不言外。亦未可以言外而不言内。有曰制之于外。以安其内者。岂不以自外至者言之乎。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所以养其外。淫乐慝礼。不接心𧗱。所以养其内。兼内外说得备。台应问何以曰久而诚。答曰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久久积功。然后可以言诚。诚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斯可谓之仁。岂略绰可做底乎。郑五锡问知诱物化。何独言于听箴。李震相曰感于物而动。惟在于听。故独于听箴言之。讲长曰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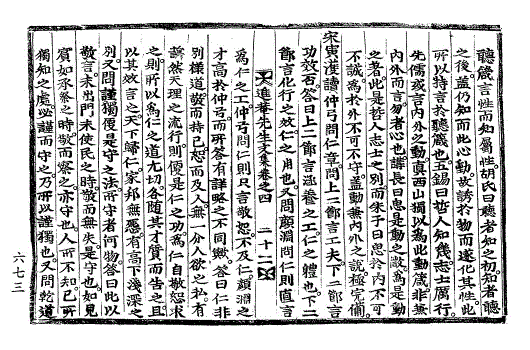 听箴言性而知属性。胡氏曰听者知之初。知者听之后。盖仍知而此心动。故诱于物而遂化其性。此所以特言于听箴也。五锡曰哲人知几。志士厉行。先儒或言内外之动。真西山独以为此动箴。非兼内外而言。勿者心也。讲长曰思是动之微。为是动之著。此是哲人志士之别。而朱子曰思于内不可不诚。为于外不可不守。盖动兼内外之说。极完备。
听箴言性而知属性。胡氏曰听者知之初。知者听之后。盖仍知而此心动。故诱于物而遂化其性。此所以特言于听箴也。五锡曰哲人知几。志士厉行。先儒或言内外之动。真西山独以为此动箴。非兼内外而言。勿者心也。讲长曰思是动之微。为是动之著。此是哲人志士之别。而朱子曰思于内不可不诚。为于外不可不守。盖动兼内外之说。极完备。宋寅濩读仲弓问仁章。问上二节言工夫。下二节言功效否。答曰上二节言涵养之工。仁之体也。下二节言化行之效。仁之用也。又问颜渊问仁则直言为仁之工。仲弓问仁则只言敬恕。不及仁。颜渊之才高于仲弓。而所答有详略之不同欤。答曰仁非别样道。敬而持己。恕而及人。无一分人欲之私。有蔼然天理之流行。则便是仁之功。为仁自敬恕求之。则所以为仁之道尤切。各随其才质而告之。且以其效言之。天下归仁。家邦无怨。有高下浅深之别。又问谨独便是守之法。所守者何物。答曰此以敬言。未出门未使民之时。敬而无失。是守也。如见宾如承祭之时。敬而察之。亦守也。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处。必谨而守之。乃所以谨独也。又问乾道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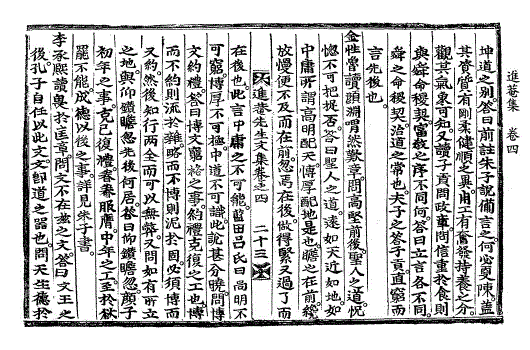 坤道之别。答曰前注朱子说备言之。何必更陈。盖其资质有刚柔健顺之异。用工有奋发持养之分。观其气象可知。又读子贡问政章。问信重于食则与舜命稷契。富教之序不同何。答曰立言各不同。舜之命稷契。治道之常也。夫子之答子贡。直穷而言先后也。
坤道之别。答曰前注朱子说备言之。何必更陈。盖其资质有刚柔健顺之异。用工有奋发持养之分。观其气象可知。又读子贡问政章。问信重于食则与舜命稷契。富教之序不同何。答曰立言各不同。舜之命稷契。治道之常也。夫子之答子贡。直穷而言先后也。金性鲁读颜渊喟然叹章。问高坚前后。圣人之道。恍惚不可把捉否。答曰圣人之道。远如天近如地。如中庸所谓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是也。瞻之在前。才放慢便不及而在前。忽焉在后。做得紧又过了而在后也。此言中庸之不可能。蓝田吕氏曰高明不可穷。博厚不可极。中道不可识。此说甚分晓。问博文约礼。答曰博文穷格之事。约礼克复之工也。博而不约则流于杂。略而不博则泥于固。必须博而又约。然后知行两全而可以无弊。又问如有所立之地。与仰钻瞻忽先后何居。答曰仰钻瞻忽。颜子初年之事。克己复礼。眷眷服膺。中年之工。至于欲罢不能。成德以后之事。详见朱子书。
李承熙读畏于匡章。问文不在玆之文。答曰文王之后。孔子自任以此文。文即道之器也。问天生德于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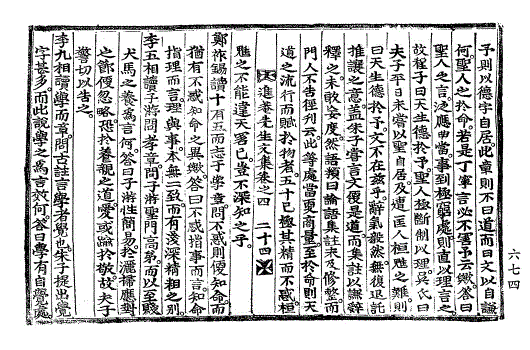 予则以德字自居。此章则不曰道而曰文以自谦何。圣人之于命。若是丁宁言必不害予云欤。答曰圣人之言。泛应曲当。事到极穷处。则直以理言之。故程子曰天生德于予。圣人极断制以理。吴氏曰夫子平日未尝以圣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难。则曰天生德于予。文不在玆乎。辞气毅然。无复退托推让之意。盖朱子尝言文便是道。而集注以谦辞释之。未敢妄度。然语类曰论语集注未及修整。而门人不告径刊云。此等处当更商量。至于命则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五十已极其精而不惑。桓魋之不能违天害己。岂不深知之乎。
予则以德字自居。此章则不曰道而曰文以自谦何。圣人之于命。若是丁宁言必不害予云欤。答曰圣人之言。泛应曲当。事到极穷处。则直以理言之。故程子曰天生德于予。圣人极断制以理。吴氏曰夫子平日未尝以圣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难。则曰天生德于予。文不在玆乎。辞气毅然。无复退托推让之意。盖朱子尝言文便是道。而集注以谦辞释之。未敢妄度。然语类曰论语集注未及修整。而门人不告径刊云。此等处当更商量。至于命则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五十已极其精而不惑。桓魋之不能违天害己。岂不深知之乎。郑祚锡读十有五而志于学章。问不惑则便知命。而犹有不惑知命之异欤。答曰不惑指事而言。知命指理而言。理与事。本无二致。而有浅深精粗之别。
李五相读子游问孝章。问子游圣门高弟。而以至贱犬马之养为言何。答曰子游性简易。于洒扫应对之节便忽略。恐于养亲之道。爱或踰于敬。故夫子警切以告之。
李九相读学而章。问古注言学者觉也。朱子提出觉字甚多。而此说学之为言效何。答曰学有自觉处。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5H 页
 有效人处。又问首篇三章必言三不亦何。答曰文之下字。如人之发语。语声低微则不足以耸动人听。此三不亦字甚有力。足使人鼓动兴起也。
有效人处。又问首篇三章必言三不亦何。答曰文之下字。如人之发语。语声低微则不足以耸动人听。此三不亦字甚有力。足使人鼓动兴起也。宋来钦读泰伯至德章。问太王仁人也。观于去豳之事可知。而集注言剪商之志何。答曰然。吾亦寻常未晓也。陈仲亨疑而问朱先生。先生曰若无此事。岂肯自诬其祖。肤浅后生。何敢疑之。
郑在卨读子曰道千乘之国章。问道字训治。愿闻其义。答曰道者治之理也。主心而言。又问圣人之言浅近云。而此章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答曰此三节。皆非高远难行之事。故曰至浅曰至近。然圣人之言。浅而至深。近而该远。以推其极则尧舜之治。亦不过此。又读慎终追远章。问民德归厚之道。不于养生言之。而必言慎终追远何。答曰不但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凡于事生之道。下民犹可企而及之。而安能知夫慎其终追其远乎。必推说得丧祭大节。以明慎礼报本。然后民可以知德之厚矣。又问送终非所敢忽。而今曰易忽何。郑五锡答曰上古不葬。其后葬亦不封不隧。至孔子然后曰我东西南北之人。始封树。礼文之未备。人情之易忽。可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5L 页
 想得。
想得。郑五锡读为人也孝弟章。李震相曰孝弟而犯上者。余于王祥验之矣。郑五锡曰王祥之孝。孝则至矣。而谓之合于圣人所谓孝之道则未也。此一节之孝。岂可与论于时中之道乎。李又问由孝弟似可以至仁。而曰非也何。郑答曰孝弟仁之一事。而曰由孝弟至仁。则仁与孝弟。却是二致。故曰非也。
进奄(一作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星山裴氏族谱序
人之有身。皆本之祖先。如水流而派分。如木敷而条达。虽百千散殊。其源其本。一而已矣。然而人不能察其理明其道。则亲属竭昭穆不明。与路人无异也。是以昔周盛时。小史氏掌邦国之志。以系其世。以辨其族。以展其亲。此谱牒之所由起。而后世欧阳氏苏氏之所以仿其事。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也。余观裴氏之氏星山者。槩千百计。苟非令德之滋润。名义之扶树。则安能源远而流长。根厚而条达如是哉。汉祗长公降于鸡林之明活山。为加利部长。多䤋捷功。儒理王赐姓裴。即六部大姓之一。而事载东史。其后太史武烈公。逐弓裔翊丽祖策首勋。享太祖庙庭。院在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6H 页
 太白城。屡传至兴安君。选参翰苑。精研箕范戴礼思传等书。此其最著也。入我朝尚书公历读书堂宝文直学。以学业传家。花堂公官亚铨。与圃隐阳村为道义交。世称关西夫子。司谏直学公。俱以文章孝友著。贞节公录开国元勋官首揆。式至今千有馀年。各派闻孙。不能尽录。而勋业之翊戴。名节之赫烈。道学之传授。秩然为东国之著姓。何其伟哉。后孙贞祚甫。述小史氏故事。刊星山谱一本。致书于墧。以求其弁文。遂感其意。以不逮之言赘之。昔张公艺九世同居。而以百忍字做去。浦江郑湜十世同居。而以勿听妇言为家范。斯二言者。足为后人之矜式。可不念哉。凡子孙虽至百世之远。以祖先视之。则均之为一体。体此意而勉之以仁厚之德。持之以谦让之风。溯其源而达其本。则所以绳前启后者。无穷期矣。
太白城。屡传至兴安君。选参翰苑。精研箕范戴礼思传等书。此其最著也。入我朝尚书公历读书堂宝文直学。以学业传家。花堂公官亚铨。与圃隐阳村为道义交。世称关西夫子。司谏直学公。俱以文章孝友著。贞节公录开国元勋官首揆。式至今千有馀年。各派闻孙。不能尽录。而勋业之翊戴。名节之赫烈。道学之传授。秩然为东国之著姓。何其伟哉。后孙贞祚甫。述小史氏故事。刊星山谱一本。致书于墧。以求其弁文。遂感其意。以不逮之言赘之。昔张公艺九世同居。而以百忍字做去。浦江郑湜十世同居。而以勿听妇言为家范。斯二言者。足为后人之矜式。可不念哉。凡子孙虽至百世之远。以祖先视之。则均之为一体。体此意而勉之以仁厚之德。持之以谦让之风。溯其源而达其本。则所以绳前启后者。无穷期矣。锦西集序
公。墧先执也。墧自龆龀。望公之颜范。棣棣威仪。恍然如腾海之皓月。浴潭之芙蕖。言笑风旨。动人四座。扬扢往牒。宛复睹左史倚相。心常景慕不已。及弁趍叨轩屏。诸子侍立。拱手竦息。伧隶入门。不笠不敢。始叹家行之检柙。不止为表著之威仪也。今读公之状。笃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6L 页
 于孝养。渔猎而供旨。一日举网不得鱼。茫然而归。道遇伏雉之异。拱而馈之。与冰鲤幕雀同其感。又不啻家行之检柙也。日其孙止铉。奉遗集诿余而叹曰。吾先子严于韬晦。凡于著述。辄削不弆。早孤馀生。述诸父遗志。与宗侄海渐。搜得若干编。直不过嵩泰之一毫芒。而欲寿其传。奉质于世好之门。愿得勘定而弁其首。余闻而伤感曰然。吾念先君之思。以勖寡昧。未可以耄昏文拙逡巡引却。遂盥而读之。文法冲澹活络。其味渊永。其论平正。非后世之役于文者攰而奇巧棘而险怪者类也。至于词律。萧洒雅亮。颇有陆务观调格。及疾革扶以坐。口授二绝于仲氏令公。即正席而终。其诗曰俗累如今初脱屣。飘然仙去十洲乡。又曰没宁生顺任西铭。斯可验公之不以死生动其心也。朱夫子曰文者道之枝叶。道非崖异绝俗之事。惟在日用彝伦之行。向所谓孝养之感物诚也。家行之检柙教也。威仪之表著文也。君子之道。不越乎是。以公博识。宜其文之烨然条畅。而每文结语。辄有谦谦退让之意。可谓文质彬彬矣。不觉钦叹而为之序。
于孝养。渔猎而供旨。一日举网不得鱼。茫然而归。道遇伏雉之异。拱而馈之。与冰鲤幕雀同其感。又不啻家行之检柙也。日其孙止铉。奉遗集诿余而叹曰。吾先子严于韬晦。凡于著述。辄削不弆。早孤馀生。述诸父遗志。与宗侄海渐。搜得若干编。直不过嵩泰之一毫芒。而欲寿其传。奉质于世好之门。愿得勘定而弁其首。余闻而伤感曰然。吾念先君之思。以勖寡昧。未可以耄昏文拙逡巡引却。遂盥而读之。文法冲澹活络。其味渊永。其论平正。非后世之役于文者攰而奇巧棘而险怪者类也。至于词律。萧洒雅亮。颇有陆务观调格。及疾革扶以坐。口授二绝于仲氏令公。即正席而终。其诗曰俗累如今初脱屣。飘然仙去十洲乡。又曰没宁生顺任西铭。斯可验公之不以死生动其心也。朱夫子曰文者道之枝叶。道非崖异绝俗之事。惟在日用彝伦之行。向所谓孝养之感物诚也。家行之检柙教也。威仪之表著文也。君子之道。不越乎是。以公博识。宜其文之烨然条畅。而每文结语。辄有谦谦退让之意。可谓文质彬彬矣。不觉钦叹而为之序。复窝集序
人受天地之中。眇然一身。列为三才。苟知人之所以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7H 页
 与天地参焉。则人岂可以轻浅之哉。天地不外于吾身。而道必在于日用彝伦。故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仁之本。盖心之德爱之理。推于人及于物。而与天地为一也。人之名义。顾不重且大欤。晋阳处士复窝河公。奋起陆海之滨。慨然有感于天地之阳复。而题其窝曰复。其言曰人于天地。参为三才。有天道有地道。而人不能行人道则可耻之甚。遂书人字于座右以自警。又恒言曰孝弟人伦之本。公其可谓窥见天人之奥。而能识天彝人道在日用常行之中矣。与谈玄好自高。游骑出太远。沉沦于漭荡之域。而卒无得者。其得失真妄。果何如哉。公事亲孝。亲病而躬执炊爨。没而致礼丧祭。事兄如温公之于伯康。爱敬备至。及菊潭公没。所尝手植菊。太半枯死。公文以吊之。枯者复生。呜呼。苟非天显之情。蔼然呈露。物之感应。安能若是灵异。孝之推仁之及。亦无所不周。见贫人之丧。贩牛而葬之。遇野人之猎。买雉而扬之。族人失学则引而敩之。丐人失所则馆而饷之。盖其温柔慈良。得于天者甚厚。而埙篪讲刮。发于学者较多矣。圣贤文字。无所不读。而尤好洛闽之书。朋友交际。泛爱容众。而必择仁贤之人。与立斋
与天地参焉。则人岂可以轻浅之哉。天地不外于吾身。而道必在于日用彝伦。故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仁之本。盖心之德爱之理。推于人及于物。而与天地为一也。人之名义。顾不重且大欤。晋阳处士复窝河公。奋起陆海之滨。慨然有感于天地之阳复。而题其窝曰复。其言曰人于天地。参为三才。有天道有地道。而人不能行人道则可耻之甚。遂书人字于座右以自警。又恒言曰孝弟人伦之本。公其可谓窥见天人之奥。而能识天彝人道在日用常行之中矣。与谈玄好自高。游骑出太远。沉沦于漭荡之域。而卒无得者。其得失真妄。果何如哉。公事亲孝。亲病而躬执炊爨。没而致礼丧祭。事兄如温公之于伯康。爱敬备至。及菊潭公没。所尝手植菊。太半枯死。公文以吊之。枯者复生。呜呼。苟非天显之情。蔼然呈露。物之感应。安能若是灵异。孝之推仁之及。亦无所不周。见贫人之丧。贩牛而葬之。遇野人之猎。买雉而扬之。族人失学则引而敩之。丐人失所则馆而饷之。盖其温柔慈良。得于天者甚厚。而埙篪讲刮。发于学者较多矣。圣贤文字。无所不读。而尤好洛闽之书。朋友交际。泛爱容众。而必择仁贤之人。与立斋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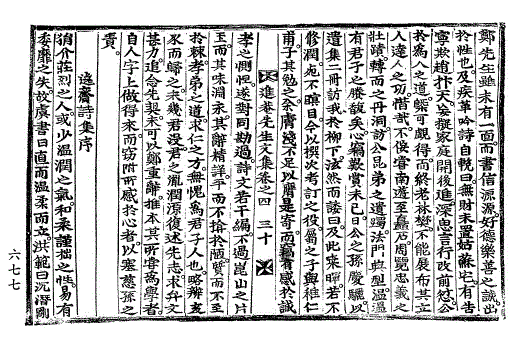 郑先生虽未有一面。而书信源源。好德乐善之诚。出于性也。及疾革吟诗自挽曰。无财未置姑苏宅。有告宁欺赵抃天。妄拟家庭开后进。深思言行改前愆。公于为人之道。槩可觑得。而终老林樊。不能展布其立人达人之功。惜哉。不佞尝南游至矗石。周览忠义之壮迹。转而之丹洞。访公昆弟之遗躅。法门典型。温温有君子之剩馥矣。心窃叹赏未已。日公之孙庆骊。以遗集二册访我于柳下。泫然而诿曰。及此桑晖。若不修润。死不瞑目。今以撰次考订之役。属之子与稚仁甫。子其勉之。余肤浅不足以膺是寄。而窃有感于诚孝之恻怛。遂对同勘过。诗文若干编。不过昆山之片玉。而其味渊永。其辞精详。平而不掩于陋。质而不至于棘。孝弟之道。求仁之方。无愧为君子人也。略辨亥豕而归之。未几君没。君之胤润源复述先志。求弁文甚力。追念先契。未可以郑重辞。推本其所尝为学者。自人字上做得来。而窃附所感于心者。以塞慈孙之责。
郑先生虽未有一面。而书信源源。好德乐善之诚。出于性也。及疾革吟诗自挽曰。无财未置姑苏宅。有告宁欺赵抃天。妄拟家庭开后进。深思言行改前愆。公于为人之道。槩可觑得。而终老林樊。不能展布其立人达人之功。惜哉。不佞尝南游至矗石。周览忠义之壮迹。转而之丹洞。访公昆弟之遗躅。法门典型。温温有君子之剩馥矣。心窃叹赏未已。日公之孙庆骊。以遗集二册访我于柳下。泫然而诿曰。及此桑晖。若不修润。死不瞑目。今以撰次考订之役。属之子与稚仁甫。子其勉之。余肤浅不足以膺是寄。而窃有感于诚孝之恻怛。遂对同勘过。诗文若干编。不过昆山之片玉。而其味渊永。其辞精详。平而不掩于陋。质而不至于棘。孝弟之道。求仁之方。无愧为君子人也。略辨亥豕而归之。未几君没。君之胤润源复述先志。求弁文甚力。追念先契。未可以郑重辞。推本其所尝为学者。自人字上做得来。而窃附所感于心者。以塞慈孙之责。逸斋诗集序
狷介庄烈之人。或少温润之气。和柔谨拙之性。易有委靡之失。故虞书曰直而温柔而立。洪范曰沉潜刚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8H 页
 克。高明柔克。盖刚柔兼济。宽猛夹持。然后言发于中而不有偏陂之患矣。余少而遌金君逸齐于八莒之石门。其色温其貌柔。眉睫之间。煞有高明之气。而粥粥若无所能。视世之衒而自高者。亦远矣。心窃异之。后四十馀年。其弟在昊甫。持公诗集。呜咽而语曰先兄遗墨。不止是戛戛。而尽烂于郁攸。遂博蒐于知旧。收拾于弊簏。乃得诗几编诔文几首。未足为泰华之一芒毫。然欲得立言之文以弁之。而先兄隐而不显。知者惟吾子而已。子其勿辞。余三辞而不获。就考其诗。淡而章简而温。韵致高古。意趣清远。发于思声于心者。不直温柔敦厚。而往往激昂慷慨。有高亢不俗之语。且其墓志曰对人雍容逊顺。而见不是处。必峻责。性甚拙而不阿附于势利。始识向之识公。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也。公岂非温而能直柔而能立。沉潜而刚克。高明而柔克者乎。余病柔恶。致力克将去。而衰暮未能。多君而序之。
克。高明柔克。盖刚柔兼济。宽猛夹持。然后言发于中而不有偏陂之患矣。余少而遌金君逸齐于八莒之石门。其色温其貌柔。眉睫之间。煞有高明之气。而粥粥若无所能。视世之衒而自高者。亦远矣。心窃异之。后四十馀年。其弟在昊甫。持公诗集。呜咽而语曰先兄遗墨。不止是戛戛。而尽烂于郁攸。遂博蒐于知旧。收拾于弊簏。乃得诗几编诔文几首。未足为泰华之一芒毫。然欲得立言之文以弁之。而先兄隐而不显。知者惟吾子而已。子其勿辞。余三辞而不获。就考其诗。淡而章简而温。韵致高古。意趣清远。发于思声于心者。不直温柔敦厚。而往往激昂慷慨。有高亢不俗之语。且其墓志曰对人雍容逊顺。而见不是处。必峻责。性甚拙而不阿附于势利。始识向之识公。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也。公岂非温而能直柔而能立。沉潜而刚克。高明而柔克者乎。余病柔恶。致力克将去。而衰暮未能。多君而序之。性理类纂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欲识天地万物之理。而不识腔子里所赋之心之为何物。则是舍近而求诸远。遗本而探其末者也。乌可乎哉。必欲究是心之所以盛贮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8L 页
 敷施。则理气相合而不相杂。体用相须而不相离。天命气质之性。四端七情之感。志意思虑之界分。忠信诚敬之名目。以至存养省察之工。读书为学之方。各有地头。而穷本极源。混合说去。则人物动植。莫不有是理。格致诚正。毫缕分析。则精粗显微。亦未可以含糊鹘突也。沉潜体验。知及仁守。而不有一息之间断。真积力久。身润体胖。而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尧舜孔孟之道。濂洛关闽之学。不出吾躯壳中一心。而天地万物之理。亦可以贯彻融释矣。然而知见庸钝。学识颛劣。傍无师友之益。居无书册之备。平生非不知此事之为可乐。而依违不振。未能造一分。至于身分上森然所具之物。亦未得其苗脉蹊径矣。是以略述宋朝群哲之论。我朝诸贤之语。随手劄录。汇分类聚。以为晚年省览之资。此实犯朱夫子好径欲速之诫。然若仍是而加切问近思之工。不求之漭荡空虚之域。则于沿流溯源之道。庶或不无少补云尔。
敷施。则理气相合而不相杂。体用相须而不相离。天命气质之性。四端七情之感。志意思虑之界分。忠信诚敬之名目。以至存养省察之工。读书为学之方。各有地头。而穷本极源。混合说去。则人物动植。莫不有是理。格致诚正。毫缕分析。则精粗显微。亦未可以含糊鹘突也。沉潜体验。知及仁守。而不有一息之间断。真积力久。身润体胖。而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尧舜孔孟之道。濂洛关闽之学。不出吾躯壳中一心。而天地万物之理。亦可以贯彻融释矣。然而知见庸钝。学识颛劣。傍无师友之益。居无书册之备。平生非不知此事之为可乐。而依违不振。未能造一分。至于身分上森然所具之物。亦未得其苗脉蹊径矣。是以略述宋朝群哲之论。我朝诸贤之语。随手劄录。汇分类聚。以为晚年省览之资。此实犯朱夫子好径欲速之诫。然若仍是而加切问近思之工。不求之漭荡空虚之域。则于沿流溯源之道。庶或不无少补云尔。古岩序
藏古山人。徒读古人书。谩不识今之俗尚。故发一言做一事。人必局局然笑之。然性胶固黏滞。不能俯仰于世。日宋君肃显。与同志者语曰我自号古岩。余闻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9H 页
 而笑曰子何居今而好古也。举折臂而戒之。肃显辴然而笑。噫我知之矣。子必笑夫今之笑古者之笑乎。虽然吾与子俱有好古之实。则笑者诚妄矣。徒窃好古之名。则子之笑。反为笑者之所笑矣。盍反身而求之。吾观子之貌听子之言。不脆蜡而碨磊。不妩媚而硬直。发于文咏于诗者。又奇伟苍健。宜其寡合于今而安于古也。然犹或有未尽分于吾心者。则以吾之不逮。顾其号而思其义。彼壁立之岩。卓卓乎颓波绝壑之滨。未尝摧折而磨灭之。其视世之随风而偃遇涛而齧者。岂不诚巍然丈夫之志节哉。子虽处𤱶亩忍穷饿。而嚣嚣然古之人古之人。实心做将去。则人必高山仰止。彼巉岩之石。亦必语曰宋肃显不负余矣。
而笑曰子何居今而好古也。举折臂而戒之。肃显辴然而笑。噫我知之矣。子必笑夫今之笑古者之笑乎。虽然吾与子俱有好古之实。则笑者诚妄矣。徒窃好古之名。则子之笑。反为笑者之所笑矣。盍反身而求之。吾观子之貌听子之言。不脆蜡而碨磊。不妩媚而硬直。发于文咏于诗者。又奇伟苍健。宜其寡合于今而安于古也。然犹或有未尽分于吾心者。则以吾之不逮。顾其号而思其义。彼壁立之岩。卓卓乎颓波绝壑之滨。未尝摧折而磨灭之。其视世之随风而偃遇涛而齧者。岂不诚巍然丈夫之志节哉。子虽处𤱶亩忍穷饿。而嚣嚣然古之人古之人。实心做将去。则人必高山仰止。彼巉岩之石。亦必语曰宋肃显不负余矣。洪起八字序
古礼宾降阶而字之。春秋因其行事之美恶而贵贱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仅十有二人。其礼重。其义极尊贵也。而后世礼弊教弛。以表德视文具。不思所以顾名之义者滔滔。日南阳洪君起八。请字于余。又求其辞。苟不志于古人礼祝之意。而必践其所命之旨。何必请于四百里外朝暮之人哉。乃取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79L 页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义字之曰文振。文公之文。如风樯阵马。扫秕糠于下世。又能因文悟道。可谓文章中杰然者。然其言曰文者贯道之器。盖不知文之为道之枝叶。而乃以为贯道之具。是文自文道自道。而非真知道之文。是以朱夫子辟之廓如。余之以文振字子者。非要振韩子之文。要以思朱夫子辟之之意。而以真文而振之也。文振勉之哉。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义字之曰文振。文公之文。如风樯阵马。扫秕糠于下世。又能因文悟道。可谓文章中杰然者。然其言曰文者贯道之器。盖不知文之为道之枝叶。而乃以为贯道之具。是文自文道自道。而非真知道之文。是以朱夫子辟之廓如。余之以文振字子者。非要振韩子之文。要以思朱夫子辟之之意。而以真文而振之也。文振勉之哉。晚学堂集序
不佞尝读许文正公书。至星山裴氏忠孝烈三纲并萃于一室四世。不觉竖义肚而𢥠然起敬矣。近又闻以晚学先生学问忠义。姜左揆劄奏。蒙 赠都宪祭酒之职。呜呼。先生巍然树立于三纲四世之绪。可谓邓林灵根。世世益昌矣。后孙升喜甫。奉遗集三册及貤赠颠末。款柳下而诿之曰。幸有以删正而弁其首。余辞而后盥读。戊午封事凡五千馀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而次言敬义夹持。终言箕田周井之法。言论简当。文章平稳。有真正君子之风。丁丑下城之后。慨然和晋徵士归去来辞。隐遁于金陵之万历洞。再辞祠官之禄。每念 显皇帝怙冒之恩。潸然出涕而赋诗。有平生壮志老蹉跎。期扫腥膻岂有他之句。此与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0H 页
 胡澹庵斩桧之书。鲁仲连却秦之言。同一关棙。宜其褒奖于尊周之录也。然先生之道。未可以一节论。学问明正。义理森严。非俗儒肤浅之见所可窥觑。何敢赞辞于其间。略加丁乙而叙之。以寓高山景行之思云尔。
胡澹庵斩桧之书。鲁仲连却秦之言。同一关棙。宜其褒奖于尊周之录也。然先生之道。未可以一节论。学问明正。义理森严。非俗儒肤浅之见所可窥觑。何敢赞辞于其间。略加丁乙而叙之。以寓高山景行之思云尔。忧堂实记序
先生 太宗朝名臣也。以松隐为父。以圃隐为师。兼与三弟有四珠之称。及擢第参瀛选。历典翰补二郡。著见于世。未免威凤之一羽。而卞黄二贤相。皆拟汉之董子。舆览人物篇备言王佐之才。此其先生之大致。而惜其遗文世远断烂。诗九章居家诫考绩策各一而已。然忠义之感。孝友之敦。公明之见。炳朗于句语之间。足以行于家推于国。而绰绰然有馀裕矣。昔孟襄阳绝调逸响。散逸殆尽。而李东洲敏求曰微云过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联。足与天壤俱弊。盖文不在多寡。而彼之萧雅风致。曷足以喻此集之道义峥嵘哉。是以文章德望。不止于先生一身。而传之三世。名登竹帛。义倬霄汉者。合至十有四士。斯可验邓林之灵根也。后孙时默。吾友也。神交意寄。信如金石。使其族弟箕默。致书而求其弁。耄昏精力。不足以膺是寄。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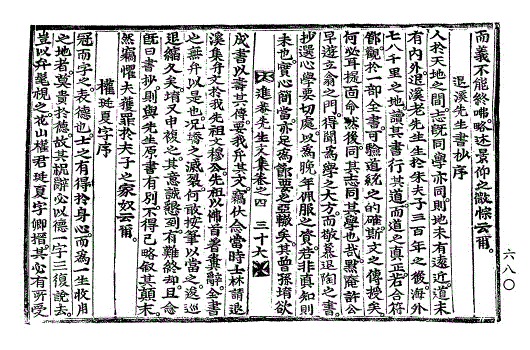 而义不能终咈。略述景仰之微悰云尔。
而义不能终咈。略述景仰之微悰云尔。退溪先生书抄序
人于天地之间。志既同学亦同。则地未有远近。道未有内外。退溪老先生生于朱夫子三百年之后。海外七八千里之地。读其书行其道。而道之真正。若合符节。观于一部全书。可验道统之的确。斯文之传授矣。何必耳提面命然后。同其志同其学也哉。默庵许公早游立翁之门。得闻为学之大方。而敬慕退陶之书。抄选心学要切处。以为晚年佩服之资。若非真知则未也。实心简当。亦足为节要之亚辙矣。其曾孙堉欲成书以寿其传。要我弁其文。窃伏念当时士林请退溪集弁文于我先祖文穆公。先祖以佛首着粪辞。全书之无弁以是也。况墧之灭裂。何敢按笔以当之。逡巡退缩久矣。堉又申复之。其意诚恳到。有难终却。且念既曰书抄。则与先生原书有别。不得已略叙其颠末。然窃惧夫获罪于夫子之家奴云尔。
权珽夏字序
冠而字之。表德也。士之有得于身心。而为一生收用之地者。莫贵于德。故其祝辞必以德一字三复说去。岂以弁髦视之。花山权君珽夏字卿搢。其必有所受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1H 页
 矣。余何敢赘焉。而君往岁求其说甚勤。今又嘱昊侄而申之。吾以世交。义未可以终辞也。卿搢其勉之。君子比德于玉。玉之质。禀得来阳精之纯。铲而在山。其辉自著。琢而成器。其章瑞世。而况珽大玉而珽然无所屈。古所谓玉界尺不足以喻其美也。荐之宗庙朝廷之上。列于黼黻笙镛之间。其为象德之用。顾何如哉。余观卿搢生长诗礼之家。服袭德义之教。其色温其性栗。其言谈举止。闇然有章。信乎其人如玉矣。惜其沦落山樊。尚未能搢珽于玉墀。以展其温栗之蕴。诚可慨。然修身饬行。益复砥砺。慎勿为衒而见刖。怀而为罪。则于卿搢终身无瑕。而人必称温温维德之隅矣。何必扬廷而后谓之珽。又安知异日不为卿士而搢之哉。穷与达。本无二道。卿搢惟一其德。
矣。余何敢赘焉。而君往岁求其说甚勤。今又嘱昊侄而申之。吾以世交。义未可以终辞也。卿搢其勉之。君子比德于玉。玉之质。禀得来阳精之纯。铲而在山。其辉自著。琢而成器。其章瑞世。而况珽大玉而珽然无所屈。古所谓玉界尺不足以喻其美也。荐之宗庙朝廷之上。列于黼黻笙镛之间。其为象德之用。顾何如哉。余观卿搢生长诗礼之家。服袭德义之教。其色温其性栗。其言谈举止。闇然有章。信乎其人如玉矣。惜其沦落山樊。尚未能搢珽于玉墀。以展其温栗之蕴。诚可慨。然修身饬行。益复砥砺。慎勿为衒而见刖。怀而为罪。则于卿搢终身无瑕。而人必称温温维德之隅矣。何必扬廷而后谓之珽。又安知异日不为卿士而搢之哉。穷与达。本无二道。卿搢惟一其德。送李子闻归商山序
子闻。吾畏友也。文学行义。足以佽助。又从事于溪堂之门。闻见日益博。以面以书。讲义论礼。多有所启发矣。今乃僦屋于商山之柴桑。出幽迁乔。可谓善变也。吾闻古人送人以言。切愿慎持身择交游。读书穷理。以践其实。则虽在数百里之外。而无间于同我乡里也。勉旃勉旃。
东湖遗稿序
文之系久矣。在胜国。屡世平章。至忠宣公。巍勋茂迹。昭载太史。其旌孝文字。先师退陶先生识之。至 宣庙世。东湖公奋起倡学。自警屡十条。可见其为学之范。而当龙蛇抢攘之际。倡义殉节。余尝感其忠义。而恨不识其后孙之所在。日北青士友文应七。访我于柳下。示东湖遗迹一册而求其弁。奔走二千馀里。以图其阐幽扬潜之计。其意孝矣。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1L 页
 丹山书堂社会序
丹山书堂社会序上巳禊饮尚矣。永和癸丑。王逸少之会山阴。元礼己未。陈公廙之集洛苑。皆盛事。而后世称逸少而不称公廙何也。晋盖多清谈之士。右军之书与笔。又为俗学子所尚而然耶。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大人君子。而形于歌咏。有不愧山阴之句。伊川子为之评曰以我礼义。为昭旷之比。道艺当笔札之工。诚不愧矣。然则公廙洛社之会。过兰亭远矣。而于二子之事。显晦不同。岂后之人。乐不羁而厌绳检。习小技而忘远致之致耶。吾辈会丹山之社。既失道艺之志。又无笔札之名。而徒取春和景明之时。以窃古人游赏之趣。多见其不知量也。得不甚愧矣乎。虽然风流文物。未必
进奄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682H 页
 无于海左。而嘐嘐愿慕之心。则不在逸少而在公廙。不在公廙而在伊川之评也。诸君何居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则今日之为此说者。安知不为后日之缩鼻。而依旧用右军之豪逸耶。但永和九年周十数甲。而又值今年之癸丑。亦一奇事也。
无于海左。而嘐嘐愿慕之心。则不在逸少而在公廙。不在公廙而在伊川之评也。诸君何居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则今日之为此说者。安知不为后日之缩鼻。而依旧用右军之豪逸耶。但永和九年周十数甲。而又值今年之癸丑。亦一奇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