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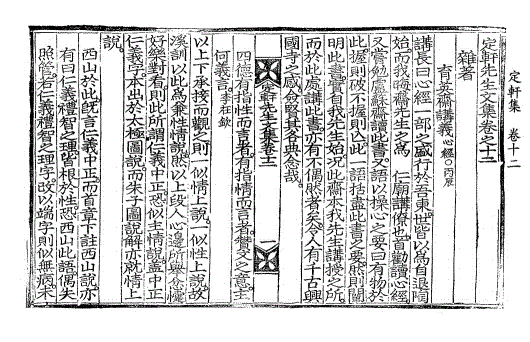 育英斋讲义(心经○丙辰)
育英斋讲义(心经○丙辰)讲长曰心经一部之盛行于吾东。世皆以为自退陶始。而我晦斋先生之为 仁庙讲僚也。首劝读心经。又尝勉卢苏斋读此书。又语以操心之要曰有物于此。握则破不握则亡。此一语括尽此书之要。然则阐明此书。实自我先生始。况此斋本我先生讲授之所。而于此处讲此书。亦有不偶然者矣。令人有千古兴国寺之感。佥贤其各典念哉。
四德有指性而言者。有指情而言者。赞文之意。主何义言。(李在钦)
以上下承接而观之。则一似情上说。一似性上说。故溪训以此为兼性情说。然以上段人心边所举忿懥好乐对看。则此所谓仁义中正。恐似主情说。盖中正仁义字。本出于太极图说。而朱子图说解亦就情上说。
西山于此。既言仁义中正。而首章下注西山说。亦有曰仁义礼智之理。皆根于性。恐西山此语。偶失照管。若仁义礼智之理字。改以端字则似无病。未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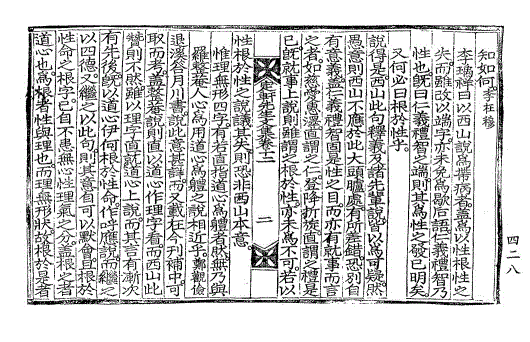 知如何。(李在穆)
知如何。(李在穆)李瑀祥曰以西山说为带病者。盖为以性根性之失。而虽改以端字。亦未免为歇后语。仁义礼智乃性也。既曰仁义礼智之端。则其为性之发已明矣。又何必曰根于性乎。
说得是。西山此句释义及诸先辈说。皆以为可疑。然愚意则西山不应于此大头胪处。有所差错。恐别自有意义。盖仁义礼智固是性之目。而亦有就事而言之者。如慈爱惠泽。直谓之仁。登降折旋。直谓之礼是已。既就事上说则虽谓之根于性。亦未为不可。若以性根于性之说议其失。则恐非西山本意。
惟理无形四字。有若直指道心为体者然。无乃与罗整庵人心为用道心为体之说相近乎。(郑观俭)
退溪答月川书。说此意甚详。而又载在今刊补中。可取而考。盖整庵说则直以道心作理字看。而西山此赞则不然。虽以理字直就道心上说。而其言有渐次有先后。既以道心伊何根于性命。作呼应说。而继之以四德。又继之以此句。则其意自可以默会。且根于性命之根字。已自不患无心性理气之分。盖根之者道心也。为根者性与理也。而理无形状。故根于是者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9H 页
 微妙而难见云尔。非谓心即是理也。
微妙而难见云尔。非谓心即是理也。溪门讲录曰自戒惧谨独。(止。)濯濯是忧。莫非一一分属人心道心说。但鸡犬之放牛羊之牧。似无分属。若以妄意分属地头。则鸡犬之放。即求放心也。自人心而收回也。牛羊之牧。即梏良心也。自道心而放去者也。如是看如何。(李能德)
林隐心学图。以求放心属之人心一边。如此说亦得。然但以孟子本文考之则鸡犬之放。亦指仁义之本心而言。则似不必指定为人心收回底。
虚灵知觉四字。形容尽心之体用。而此图又加神明二字何也。(崔世鹤)
程氏之意。非谓虚灵知觉之外。别有所谓神明也。盖言古人之形容心体者。有此多般样云尔。朱子集注心释随处各异。而有以虚灵知觉而总言之者。中庸序文是也。又有只举知觉字而言之者。虞书人道心本注是也。又有换著神明字而言之者。如孟子尽心章注是也。要之神明二字。乃虚灵知觉四个字之约说者。而不必分析看。然若分别言之则虚灵是心之体段。神明是心之妙用。故细考大学章句或问则于统说心体处着虚灵字。于单释知字处著神明字。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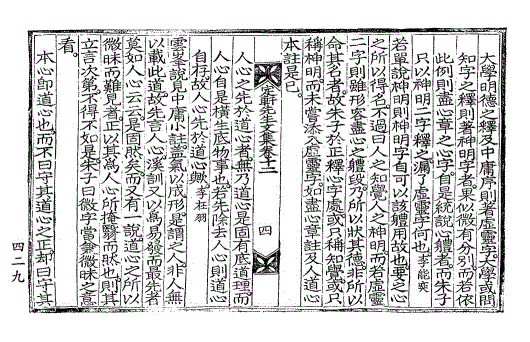 大学明德之释及中庸序则著虚灵字。大学或问知字之释则著神明字者。果似微有分别。而若依此例则尽心章之心字。自是统说心体者。而朱子只以神明二字释之。漏了虚灵字何也。(李能奕)
大学明德之释及中庸序则著虚灵字。大学或问知字之释则著神明字者。果似微有分别。而若依此例则尽心章之心字。自是统说心体者。而朱子只以神明二字释之。漏了虚灵字何也。(李能奕)若单说神明则神明字自可以该体用故也。要之心之所以得名。不过曰人之知觉人之神明。而若虚灵二字则虽形容尽心之体段。乃所以状其德。非所以命其名者。故朱子于正释心字处。或只称知觉。或只称神明。而未尝添入虚灵字。如尽心章注及人道心本注是已。
人心之先于道心者。无乃道心是固有底道理。而人心自是横生底物事也。若先除去人心则道心自存。故人心先于道心欤。(李在羽)
云峰说见中庸小注。盖气以成形。是谓之人。非人无以载此道。故先言人心。溪训又以为易发而最先者莫如人心云云。是固然矣。而又有一说。道心之所以微昧而难见者。正以其为人心所掩翳而然也。则其立言次第。不得不如是。朱子曰微字当兼微昧之意看。
本心即道心也。而不曰守其道心之正。却曰守其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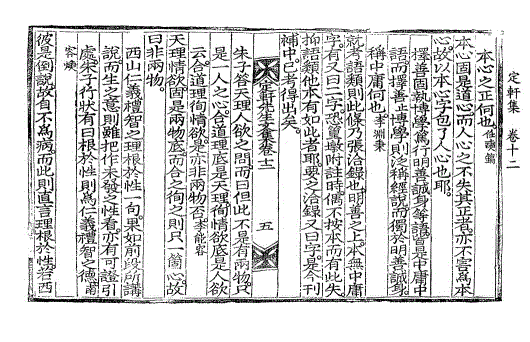 本心之正何也。(任奭镐)
本心之正何也。(任奭镐)本心固是道心。而人心之不失其正者。亦不害为本心。故以本心字包了人心也耶。
择善固执博学笃行明善诚身等语。皆是中庸中语。而择善(止)博学则泛称经说。而独于明善诚身。称中庸何也。(李渊秉)
就考语类则此条乃张洽录也。明善之上。本无中庸字。有又曰二字。恐篁墩附注时。偶不按本而有此失。抑语类他本有如此者耶。要之洽录又曰字。是今刊补中。已考得出矣。
朱子答天理人欲之问。而曰但此不是有两物。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云。合道理徇情欲。是亦非两物否。(李能容)
天理情欲。固是两物底。而合之徇之则只一个心。故曰非两物。
西山仁义礼智之理根于性一句。果如前段所讲说。而生之意则虽把作未发之性看。亦有可證引处。朱子行状有曰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南容焕)
彼是倒说。故自不为病。而此则直言理根于性。若西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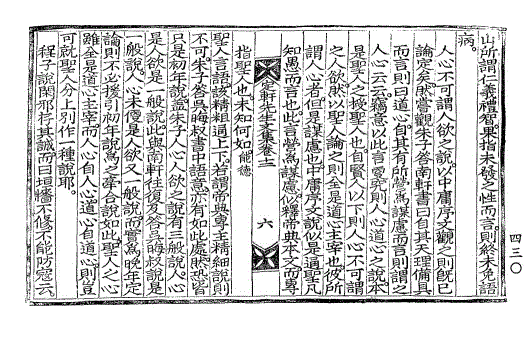 山所谓仁义礼智。果指未发之性而言。则终未免语病。
山所谓仁义礼智。果指未发之性而言。则终未免语病。人心不可谓人欲之说。以中庸序文观之则既已论定矣。然尝观朱子答南轩书曰自其天理备具而言则曰道心。自其有所营为谋虑而言则谓之人心云云。窃意以此言更究则人心道心之说。本是圣人之授圣人也。自贤人以下则人心不可谓之人欲。然以圣人论之则全是道心主宰也。彼所谓人心者。但是谋虑也。中庸序文说似是通圣凡知愚而言也。此言营为谋虑。似释帝典本文。而专指圣人也。未知何如。(能德)
圣人言语。该精粗通上下。若谓帝典专主精细说则不可。朱子答吴晦叔书中语意。亦有如此处。然恐皆只是初年说。盖朱子人心人欲之说有三般说。人心是人欲是一般说。此与南轩往复及答吴晦叔说是一般说。人心未便是人欲又一般说。而实为晚年定论则不必援引初年说为之牵合说如此。圣人之心虽全是道心主宰。而人心自人心。道心自道心。则岂可就圣人分上别作一种说耶。
程子说闲邪存其诚。而曰垣墙不修。不能防寇云。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1H 页
 垣墙是诚。寇是邪否。(李华久)
垣墙是诚。寇是邪否。(李华久)闲是修垣墙底。诚是主人翁。
常言既信。常行既谨。但用闲邪。怕他入来云者。与无射亦保之意。似不相干。而以此明彼何也。(奭镐)
常言既信常行既谨。则无所事于持守而犹自闲邪。此便是无射亦保之意。尝见语类。又有一条语。此云庸信庸谨。盛德之至。到这里不须得恁地。而犹自闲存。便是无射亦保云云。更说得分晓。
闲邪思无邪两个邪字。吴氏以正心诚意分言之。此说亦好。然妄意思无邪。是无主于内而戒其内邪之发也。闲邪。是内既有主而外邪不能入也。如是看如何。(能德)
如是看亦好。然不论内外邪。未有不由心思而发者。且凡言邪者。亦未有不自外而至者。则恐不必如是分析。
临川吴氏曰物接乎外。闲之而不干乎内。质疑以为禅家说。而先辈又以厌事绝物。反观内照斥之。然窃意草庐虽有陆学之讥而其说不应若是之差谬。抑草庐之意别有所在而然欤。(在钦)
疑得是。按芝山考误引语类一条。以明吴说之未可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1L 页
 深非。恐似得之。盖朱子既以或人防闲外物。使不得侵近之说为是。而又曰凡言邪者。皆自外至。则吴氏之意亦若是而已矣。但物字上当著外字。或物字下别添三两字然后。方可以免语病。而吴氏只泛称物。所以起后贤之疑也。又思之。吴氏之所以只称物字。亦似有意。盖其立论。以无邪之邪。作私欲恶念之邪。以闲邪之邪。作二而且杂之邪。故虽物之当应者。方其一事未了而一事又至。则亦在所闲御。此是他治疗二而且杂之方法也。非一切远事绝物之谓也。观上文内心不二不杂之语则可知其意矣。虽是如此。此是硬法。终非物来顺应底气像。味其语言则其染禅染陆之失固有在。而若其立言之本意则有如此者。
深非。恐似得之。盖朱子既以或人防闲外物。使不得侵近之说为是。而又曰凡言邪者。皆自外至。则吴氏之意亦若是而已矣。但物字上当著外字。或物字下别添三两字然后。方可以免语病。而吴氏只泛称物。所以起后贤之疑也。又思之。吴氏之所以只称物字。亦似有意。盖其立论。以无邪之邪。作私欲恶念之邪。以闲邪之邪。作二而且杂之邪。故虽物之当应者。方其一事未了而一事又至。则亦在所闲御。此是他治疗二而且杂之方法也。非一切远事绝物之谓也。观上文内心不二不杂之语则可知其意矣。虽是如此。此是硬法。终非物来顺应底气像。味其语言则其染禅染陆之失固有在。而若其立言之本意则有如此者。龟山此条论敬而必以诚心发端。有若论诚者然。未知此意如何。(能容)
诚与敬对说则诚是真实底意。敬是畏谨底意。而若单说敬字则无真心。做敬不得。而诚与敬只是一事。故杨氏说如此。
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两个道理。只是一串说。则下道理字。似是结了上段说。然照应亦有两个疑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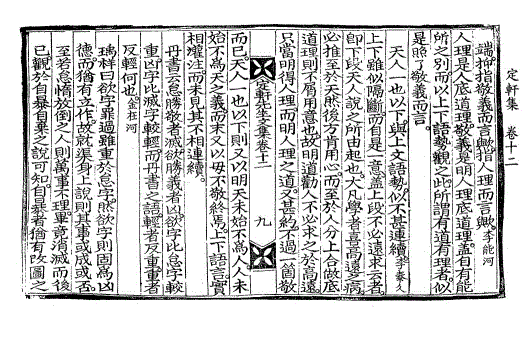 端。抑指敬义而言欤。指人理而言欤。(李能河)
端。抑指敬义而言欤。指人理而言欤。(李能河)人理是人底道理。敬义是明人理底道理。盖自有能所之别。而以上下语势观之。此所谓有道有理者。似是照了敬义而言
天人一也以下。与上文语势。似不甚连续。(李泰久)
上下虽似隔断。而自是一意。盖上段不必远求云者。即下段天人说之所由起也。大凡学者喜高远之病。必推至于天然后方肯用心。而至于人分上合做底道理则不屑用意也。故明道劝人不必求之于高远。只当明得人理。而明人理之道。又甚约。不过一个敬而已。天人一也以下则又以明天未始不为人。人未始不为天之义。而末又以毋不敬终焉。上下语言。实相灌注。而未见其不相连续。
丹书云怠胜敬者灭。欲胜义者凶。欲字比怠字较重。凶字比灭字较轻。而丹书之语。轻者反重。重者反轻何也。(金在河)
瑀祥曰欲字罪过虽重于怠字。然欲字则固为凶德。而犹有立作。故就渠身上说则其事或成或否。至若怠惰放倒之人则万事不理。毕竟消灭而后已。观于自暴自弃之说可知。自暴者犹有改图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2L 页
 望。而自弃者永无向善之路。盖自暴者强恶也。自弃者柔恶也。欲与怠正与此相类。此所以怠言灭欲言凶者欤。
望。而自弃者永无向善之路。盖自暴者强恶也。自弃者柔恶也。欲与怠正与此相类。此所以怠言灭欲言凶者欤。灭是渐次消灭底意。凶是即地凶害底意。要之怠便放倒而放倒处合说灭字。欲则违理而违理处合说凶字。今以事之成否。论凶灭两字之轻重者。似涉如何。然大槩则推说得甚好。
说只恁地说。质疑以为上说字所说。下说字说之也。则是退溪从问者论说上看。而芝山考误则以为问者但举敬直义方本文以问。而无所解说之语。则说字当作本文说看云云。窃意从溪训则语势似顺。而但问者只举本文。无所解说。而将说字作面前说话者。果如芝山所疑。(南晟焕)
取考语类则不曾将身己做之下。别有讲学等语。而又有只恁地说依旧不济事之语。以此参考则当依溪训读也明矣。此处恁地说之说字。既是从问者说而为之说。则不应同一句语。而一席上说话义有异同。盖问者举此句质问时自有说话。故朱子以为说则只如此说云。而记录者于问者说话则略之。而只录所问之句。所以致芝翁之疑。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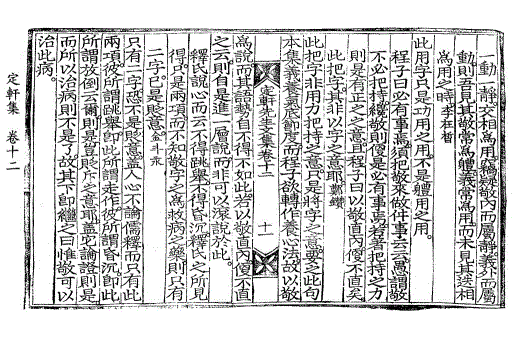 一动一静。交相为用。窃疑敬内而属静。义外而属动。则吾见其敬常为体。义常为用。而未见其迭相为用之时。(李在晰)
一动一静。交相为用。窃疑敬内而属静。义外而属动。则吾见其敬常为体。义常为用。而未见其迭相为用之时。(李在晰)此用字只是功用之用。不是体用之用。
程子曰必有事焉。须把敬来做件事云云。愚谓敬不必把持。才敬则便是必有事焉。若著把持之力则是有正之之意。且程子曰以敬直内。便不直矣。此把字。其非以字之意耶。(郑钻)
此把字非用力把持之意。只是将字之意。要之此句本集义养气底节度。而程子欲转作养心法。故以敬为说。而其语势自不得不如此。若以敬直内。便不直之云。则自是进一层说。而非可以滚说于此。
释氏说心而云不得跳举。不得昏沉。释氏之所见得。只是两项。而不知敬字之为救病之药。则只有二字。已是贬意。(金斗永)
只有二字。恐不是贬意。盖人心不论儒释而只有此两项。彼所谓跳举。即此所谓走作。彼所谓昏沉。即此所谓放倒云尔。则是岂贬斥之意耶。盖它论證则是。而所以治病则不是了。故其下即继之曰惟敬可以治此病。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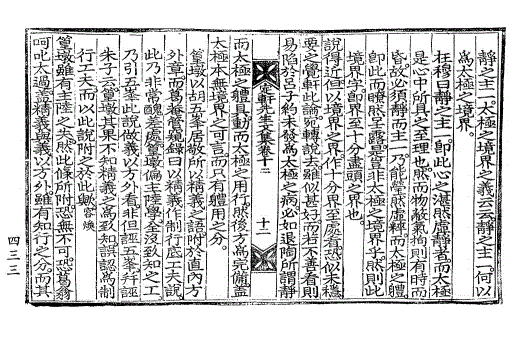 静之主一。太极之境界之义云云。静之主一。何以为太极之境界。
静之主一。太极之境界之义云云。静之主一。何以为太极之境界。在穆曰静之主一。即此心之湛然虚静者。而太极是心中所具之至理也。然而物蔽气拘则有时而昏。故必须静而主一。乃能莹然虚粹。而太极之体。即此而瞭然呈露。是岂非太极之境界乎。然则此境界字。即界至十分尽头之界也。
说得近。但以境界之界。作十分界至处看。恐似未稳。要之觉轩此论。宛转说去。虽似甚好。而若不善看则易陷于吕子约未发为太极之病。必如退陶所谓静而太极之体具。动而太极之用行。然后方为完备。盖太极本无境界之可言。而只有体用之分。
篁墩以胡五峰居敬所以精义之语。附于直内方外章。而葛庵管窥录曰以精义作制行底工夫说。此乃非常丑差处。篁墩偏主陆学。全没致知之工。乃引五峰此说做义以方外看。非但诬五峰。并诬朱子云。篁墩其果不知精义之为致知。误认为制行工夫。而以此说附之于此欤。(容焕)
篁墩虽有主陆之失。然此条所附。恐无不可。恐葛翁呵叱太过。盖精义与义以方外。虽有知行之分。而其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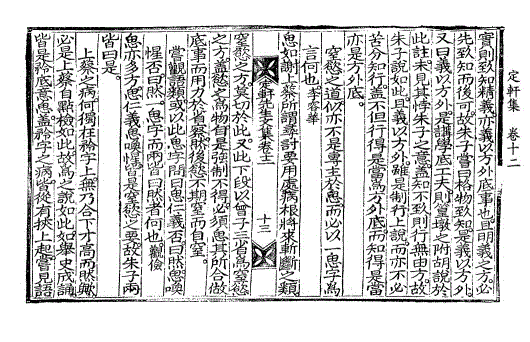 实则致知精义。亦义以方外底事也。且明义之方。必先致知而后可。故朱子尝曰格物致知。是义以方外。又曰义以方外。是讲学底工夫。则篁墩之附胡说于此注。未见其悖朱子之意。盖知不致则行无由方。故朱子说如此。且义以方外。虽是制行上说。而亦不必苦分知行。盖不但行得是当为方外底。而知得是当亦是方外底。
实则致知精义。亦义以方外底事也。且明义之方。必先致知而后可。故朱子尝曰格物致知。是义以方外。又曰义以方外。是讲学底工夫。则篁墩之附胡说于此注。未见其悖朱子之意。盖知不致则行无由方。故朱子说如此。且义以方外。虽是制行上说。而亦不必苦分知行。盖不但行得是当为方外底。而知得是当亦是方外底。窒欲之道。似亦不是专主于思。而必以一思字为言何也。(李容华)
思如谢上蔡所谓寻讨要用处病根将来斩断之类。窒欲之方。莫切于此。又此下段以曾子三省为窒欲之方。盖欲之为物。自是强制不得。必须思其所合做底事而用力于省察。然后欲不期窒而自窒。
尝观语类。或以此思字问曰思仁义否。曰然。思唤惺否。曰然。一思字而两皆曰然者何也。(观俭)
思亦多方。思仁义思唤惺。皆是窒欲之要。故朱子两皆曰是。
上蔡之病。何独在矜字上。无乃合下才高而然欤。
必是上蔡自点检如此。故为之说如此。如举史成诵。皆是矜底意思。盖矜字之病。皆从有挟上起。尝见语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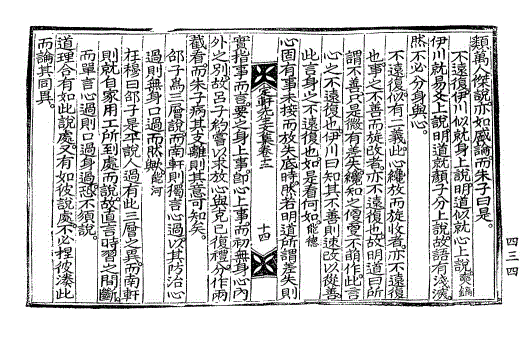 类万人杰说。亦如盛论。而朱子曰是。
类万人杰说。亦如盛论。而朱子曰是。不远复。伊川似就身上说。明道似就心上说。(奭镐)
伊川就易爻上说。明道就颜子分上说。故语有浅深。然不必分身与心。
不远复。似有二义。此心才放而旋收者。亦不远复也。事之不善而旋改者。亦不远复也。故明道曰所谓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知之便更不萌作。此言心之不远复也。伊川曰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此言身之不远复也。如是看何如。(能德)
心固有事未接而放失底时。然若明道所谓差失则实指事而言。要之身上事。即心上事。而初无身心内外之别。故吕子约尝以求放心与克己复礼。分作两截看。而朱子病其支离则其意可知矣。
邵子为三层说。而南轩则独言心过。以其防治心过则无身口过而然欤。(能河)
在穆曰邵子是平说人过有此三层之异。而南轩则就自家用工所到处而说。故直言时习之间断。而单言心过则口过身过。恐不须说。
道理合有如此说处。又有如彼说处。不必捏彼凑此而论其同异。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5H 页
 绝四以今集注看则四毋字。非禁止辞也。乃无字也。程子曰始则须绝四。横渠曰绝四自始学至成德。竭两端之教也云。则此把毋字作禁止辞看。然则朱子看作圣人上说。程张看作教人说否。(能德)
绝四以今集注看则四毋字。非禁止辞也。乃无字也。程子曰始则须绝四。横渠曰绝四自始学至成德。竭两端之教也云。则此把毋字作禁止辞看。然则朱子看作圣人上说。程张看作教人说否。(能德)毋字是禁止之辞。而圣人分上。著禁止之辞不得。故程张皆作学者用工夫看。及朱子引史记證毋为无。然后始解绝字为无之尽者。而其义始明。然以程子圣人绝此四者。何用禁止之语观之。则程子已看得出这意。
伊川天地储精之说。出于周子太极图说。然图说则先言真而后言精。此说则先言精而后言真何欤。(世鹤)
图说则从天地赋予上说下来。此论则从人物禀受上推上去。故二字先后如此。然储精之精。已包得真字。
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既曰真而静。又曰未发也五性具焉。真与五性。静与未发。同欤异欤。(李能念)
朱子曰五性即是真。未发便是静。盖此虽作两重说。而实非两截事。退溪答锦溪书。说此段甚详。而载在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5L 页
 刊补中。取考可也。
刊补中。取考可也。好学论知所往之往字。论语心经皆著往字。二程全书近思录皆著养字。以上文养其性观之。则知所养云者似是。以下文力行以求至观之则知所往云者似是。养与往。以何字为定。(李在镀)
尝考语类。朱子曰往与行字相应。恐往字为是。此论语集注之所以决作往字。但论语集注与近思录编辑。皆出于朱子之手。而两字各存。如此者当必有微意。岂以养字亦全书中一本所传。而不无旨义之可思。故两存之欤。
伊川好学论。于未发处既言五性之具。则于已发处独言七情而不及四端何欤。(能河)
能德曰是虽浑沦说。然此论本是颜子克己上说。故只就喜怒哀乐上说。
说得是。本文迁怒之怒字。自是七情之一。而要之迁怒贰过。皆是情欲炽荡之失。则此处说四端不得。
此曰不是克了己。方去复礼。而就考语类则又曰克己后又须复礼。二说不同。不知将何所适从。(朴容复)
克己了又须复礼。自是一般说。克己则礼便复。又是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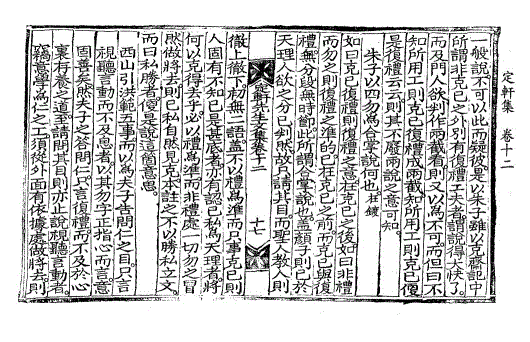 一般说。不可以此而疑彼。是以朱子虽以克斋记中所谓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工夫者。谓说得大快了。而及门人欲判作两截看。则又以为不可。而但曰不知所用工则克己复礼成两截。知所用工则克己便是复礼云云。则其不废两说之意可知。
一般说。不可以此而疑彼。是以朱子虽以克斋记中所谓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工夫者。谓说得大快了。而及门人欲判作两截看。则又以为不可。而但曰不知所用工则克己复礼成两截。知所用工则克己便是复礼云云。则其不废两说之意可知。朱子以四勿为合掌说何也。(在镀)
如曰克己复礼则复礼之意。在克己之后。如曰非礼而勿之则复礼之准的。已在克己之前。而克己与复礼。无分段无时节。此所谓合掌说也。盖颜子则已于天理人欲之分已判然。故只请其目。而圣人教人则彻上彻下。初无二语。盖不以礼为准而只事克己则人固有不知己是甚底者。亦有认己私为天理者。将何以克得去乎。必以礼为准。而非礼处一切勿之冒然做将去。则己私自然见克。本注之不以胜私立文。而曰私胜者。便是说这个意思。
西山引洪范五事。而以为夫子告问仁之目。只言视听言动而不及思者。以其勿字正指心而言。意固善矣。然夫子之答问仁。只言复礼。而不及于心里存养之道。至请问其目则亦止说视听言动者。窃意学为仁之工。须从外面有依据处做将去。则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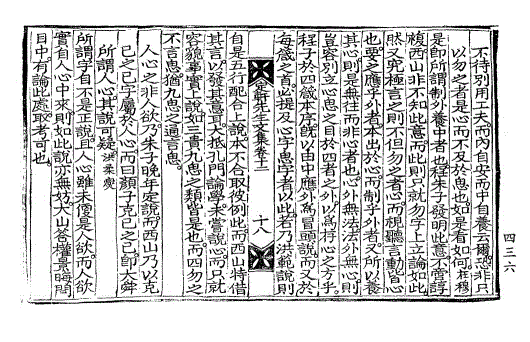 不待别用工夫。而内自安而中自养云尔。恐非只以勿之者是心而不及于思也。如是看如何。(在穆)
不待别用工夫。而内自安而中自养云尔。恐非只以勿之者是心而不及于思也。如是看如何。(在穆)是即所谓制外养中者也。程朱子发明此意。不啻谆复。西山非不知此意。而此则只就勿字上立论如此。然又究极言之则不但勿之者心。而视听言动皆心也。要之应乎外者。本出于心。而制乎外者。又所以养其心。则是无往而非心者也。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则岂容别立心思之目于四者之外。以为存心之方乎。程子于四箴本序。既以由中应外为冒头说。而又于每箴之首。必提及心字思字者以此。若乃洪范说则自是五行配合上说。本不合取彼例此。而西山特借其言。以发其意耳。大抵孔门论学。未尝说心。而只就容貌事实上说。如三贵九思之类皆是也。而四勿之不言思。犹九思之通言思。
人心之非人欲。乃朱子晚年定说。而西山乃以克己之己字属于人心。而曰颜子克己之己。即大舜所谓人心。其说可疑。(洪柔燮)
所谓字自不是正说。且人心虽未便是人欲。而人欲实自人心中来。则如此说亦无妨。大山答权景晦问目中。有论此处。取考可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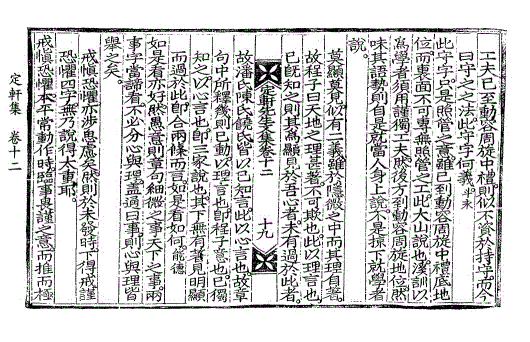 工夫已至动容周旋中礼。则似不资于持守。而今曰守之之法。此守字何义。(斗永)
工夫已至动容周旋中礼。则似不资于持守。而今曰守之之法。此守字何义。(斗永)此守字。只是照管之意。虽已到动容周旋中礼底地位。而里面不可专无照管之工。此大山说也。溪训以为学者须用谨独工夫。然后方到动容周旋地位。然味其语势则自是就当人身上说。不是掠下就学者说。
莫显莫见。似有二义。虽于隐微之中而其理自著。故程子曰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此以理言也。己既知之则其为显见于吾心者。未有过于此者。故潘氏陈氏饶氏皆以己知言。此以心言也。故章句中所释几则已动。以理言也。即程子意也。己独知之。以心言也。即三家说也。其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即合两条而言。如是看如何。(能德)
如是看亦好。然愚意则章句细微之事天下之事。两事字当谛看。不必分心与理。盖通曰事。则心与理皆举之矣。
戒慎恐惧。亦涉思虑矣。然则于未发时。下得戒谨恐惧四字。无乃说得太重耶。
戒慎恐惧。本平常动作时。临事畏谨之意。而推而极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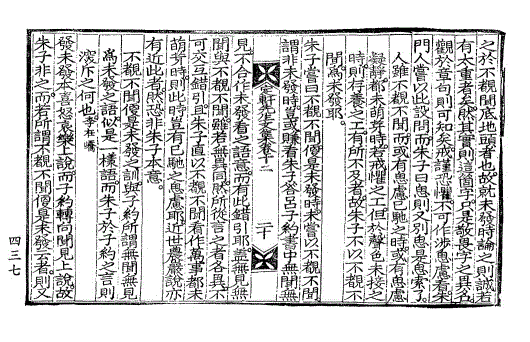 之于不睹闻底地头者也。故就未发时论之则诚若有太重者矣。然其实则这个字。只是敬畏字之异名。观于章句则可知矣。戒谨恐惧。不可作涉思虑看。朱门人尝以此设问。而朱子曰思则又别思是思索了。
之于不睹闻底地头者也。故就未发时论之则诚若有太重者矣。然其实则这个字。只是敬畏字之异名。观于章句则可知矣。戒谨恐惧。不可作涉思虑看。朱门人尝以此设问。而朱子曰思则又别思是思索了。人虽不睹不闻。而或有思虑已驰之时。或有思虑凝静。都未萌芽时。若戒惧之工。但于声色未接之时。则存养之工。有所不及者。故朱子不以不睹不闻。为未发耶。
朱子尝曰不睹不闻。便是未发时。未尝以不睹不闻。谓非未发时。岂或赚看朱子答吕子约书中无闻无见。不合作未发看之语意。而有此错引耶。盖无见无闻与不睹不闻。虽若无异同。然所从言之者各异。不可交互错引。且朱子直以不睹不闻看作万事都未萌芽时。则此时岂有已驰之思虑耶。近世农岩说亦有近此者。然恐非朱子本意。
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训。与子约所谓无闻无见为未发之语。似是一样语。而朱子于子约之言则深斥之何也。(李在峤)
发未发本喜怒哀乐上说。而子约转向闻见上说。故朱子非之。而若所谓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云者。则又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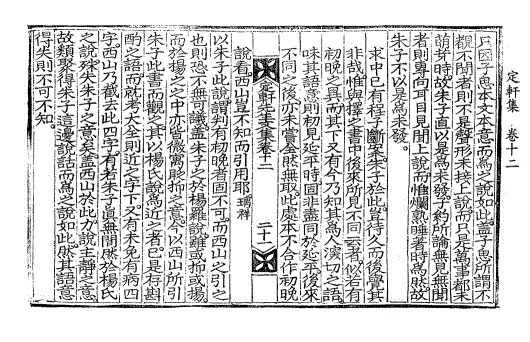 只因子思本文本意而为之说如此。盖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则不是声形未接上说。而只是万事都未萌芽时。故朱子直以是为未发。子约所论无见无闻者则专向耳目见闻上说。而惟烂熟睡著时为然。故朱子不以是为未发。
只因子思本文本意而为之说如此。盖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则不是声形未接上说。而只是万事都未萌芽时。故朱子直以是为未发。子约所论无见无闻者则专向耳目见闻上说。而惟烂熟睡著时为然。故朱子不以是为未发。求中已有程子断案。朱子于此。岂待久而后觉其非哉。惟与择之书中后来所见不同云者。似若有初晚之异。而其下又有今乃知其为人深切之语。味其语意则初见延平时。固非尽同于延平。后来不同之后。亦未尝全然无取。此处本不合作初晚说看。西山岂不知而引用耶。(瑀祥)
以朱子此说。谓判有初晚者固不可。而西山之引之也则恐不无可议。盖朱子之于杨罗说。虽或抑或扬。而于扬之之中亦皆微寓贬抑之意。今以西山所引朱子此书而观之。其以杨氏说为近之者。已是存斟酌之语。而就考大全则近之字下。又有未免有病四字。西山乃截去此四字。有若朱子真无间然于杨氏之说。殊失朱子之意矣。盖西山于此。力说主静之意。故类聚得朱子这边说话而为之说如此。然其语意得失则不可不知。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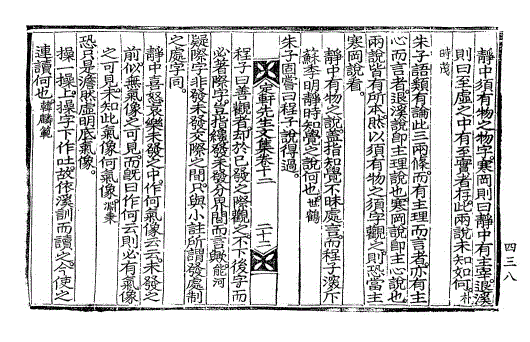 静中须有物之物字。寒冈则曰静中有主宰。退溪则曰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此两说未知如何。(朴时茂)
静中须有物之物字。寒冈则曰静中有主宰。退溪则曰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此两说未知如何。(朴时茂)朱子语类有论此三两条。而有主理而言者。亦有主心而言者。退溪说即主理说也。寒冈说即主心说也。两说皆有所本。然以须有物之须字观之。则恐当主寒冈说看。
静中有物之说。盖指知觉不昧处言。而程子深斥苏季明静时知觉之说何也。(世鹤)
朱子固尝曰程子说得过。
程子曰善观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不下后字而必著际字。岂指才发未发分界间而言欤。(能河)
疑际字非发未发交际之间。只与小注所谓发处制之处字同。
静中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作何气像云云。未发之前。似无气像之可见。而既曰作何云则必有气像之可见。未知此气像何气像。(渊秉)
恐只是澹然虚明底气像。
操一操。上操字下作吐。故依溪训而读之。今使之连读何也。(韩麟范)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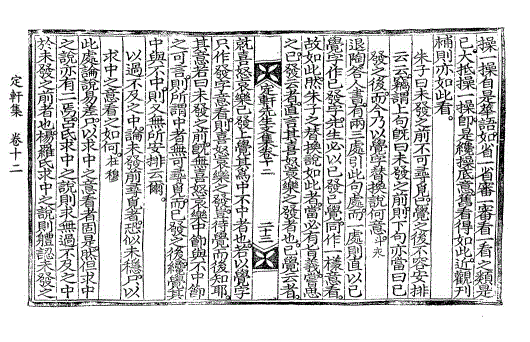 操一操自是华语。如省一省审一审看一看之类是已。大抵操一操。即是才操底意。旧看得如此。近观刊补则亦如此看。
操一操自是华语。如省一省审一审看一看之类是已。大抵操一操。即是才操底意。旧看得如此。近观刊补则亦如此看。朱子曰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云云。窃谓上句既曰未发之前。则下句亦当曰已发之后。而今乃以觉字替换说何意。(斗永)
退陶答人书。有两三处引此句处。而一处则直以已觉字作已发字。先生必以已发已觉。同作一样意看。故如此。然朱子之替换说如此者。当必有旨义。尝思之。已发云者。直言其喜怒哀乐之发者也。已觉云者。就喜怒哀乐已发上觉其为中不中者也。若以觉字只作发字意看。则喜怒哀乐之发。岂待觉而后知耶。其意若曰未发之前。既无喜怒哀乐中节与不中节之可言。则所谓中者无可寻觅。而已发之后。才觉其中与不中。则又无所安排云尔。
以过不及之中。论未发前寻觅者。恐似未稳。只以求中之意看之如何。(在穆)
此处论说易差。只以求中之意看者固是。然但求中之说亦有二焉。吕氏求中之说则求无过不及之中于未发之前者也。杨罗氏求中之说则体认未发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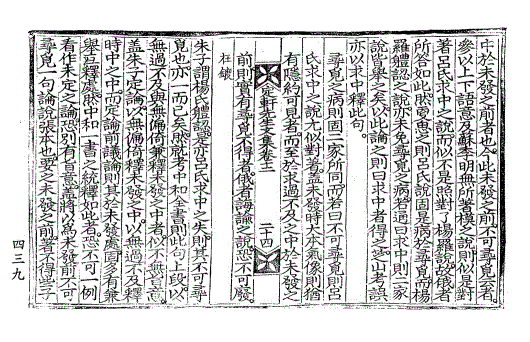 中于未发之前者也。今此未发之前。不可寻觅云者。参以上下语意及苏季明无所著模之说。则似是对著吕氏求中之说。而似不是照对了杨罗说。故俄者所答如此。然更思之则吕氏说固是病于寻觅。而杨罗体认之说。亦未免寻觅之病。若通曰求中则二家说皆举之矣。以此论之则曰求中者得之。芝山考误亦以求中释此句。
中于未发之前者也。今此未发之前。不可寻觅云者。参以上下语意及苏季明无所著模之说。则似是对著吕氏求中之说。而似不是照对了杨罗说。故俄者所答如此。然更思之则吕氏说固是病于寻觅。而杨罗体认之说。亦未免寻觅之病。若通曰求中则二家说皆举之矣。以此论之则曰求中者得之。芝山考误亦以求中释此句。寻觅之病则固二家所同。而若曰不可寻觅则吕氏求中之说尤似对著。盖未发时大本气像则犹有隐约可见者。而至于求过不及之中于未发之前。则实有寻觅不得者。俄者诲谕之说。恐不可废。(在镀)
朱子谓杨氏体认。是亦吕氏求中之失。则其不可寻觅也。亦一而已矣。然就考中和全书则此句上段。以无过不及与无偏倚兼释未发之中者。似不无旨意。盖朱子定论。以无偏倚释未发之中。以无过不及释时中之中。而定论前议论则其于未发处。固多有兼举互释处。然中和一书之统释如此者。恐不可一例看作未定之论。恐别有旨意。盖将以为未发前不可寻觅一句论说张本也。要之未发之前。著不得些子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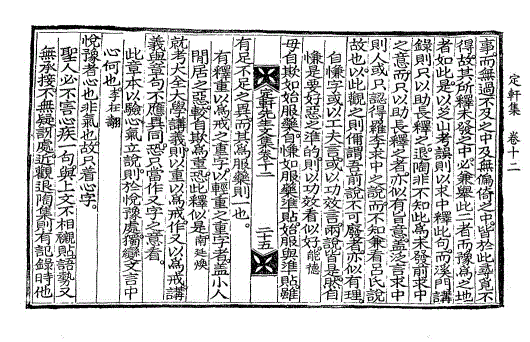 事。而无过不及之中及无偏倚之中。皆于此寻觅不得。故其所释未发之中。必兼举此二者而豫为之地者如此。是以芝山考误则以求中释此句。而溪门讲录则只以助长释之。退陶非不知此为未发前求中之意。而只以助长释之者。亦似有旨意。盖泛言求中则人或只认得罗李求中之说。而不知兼看吕氏说故也。以此观之则称谓吾前说不可废者。亦似有理。
事。而无过不及之中及无偏倚之中。皆于此寻觅不得。故其所释未发之中。必兼举此二者而豫为之地者如此。是以芝山考误则以求中释此句。而溪门讲录则只以助长释之。退陶非不知此为未发前求中之意。而只以助长释之者。亦似有旨意。盖泛言求中则人或只认得罗李求中之说。而不知兼看吕氏说故也。以此观之则称谓吾前说不可废者。亦似有理。自慊字或以工夫言。或以功效言。两说皆是。然自慊是要好恶之准的。则以功效看似好。(能德)
毋自欺如始服药。自慊如服药准贴。始服与准贴。虽有足不足之异。而其为服药则一也。
有释重以为戒之重字。以轻重之重字者。盖小人閒居之恶。较自欺为重。恐此释似是。(南廷焕)
就考大全大学讲义。则以重以为戒。作又以为戒。讲义与章句不应异同。恐只当作又字之意看。
此章本以验心气立说。则于悦豫处。独变文言中心何也。(李在翿)
悦豫者心也非气也。故只着心字。
圣人必不害心疾一句。与上文不相衬贴。语势又无承接。不无疑讶处。近观退陶集则有记录时他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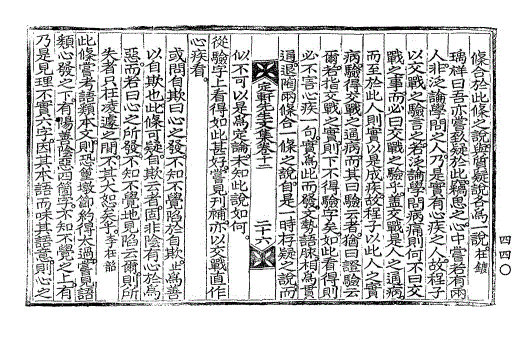 条合于此条之说。与质疑说各为一说。(在镀)
条合于此条之说。与质疑说各为一说。(在镀)瑀祥曰吾亦尝致疑于此。窃思之。心中尝若有两人。非泛论学问之人。乃是实有心疾之人。故程子以交战之验言之。若泛论学问病痛则何不曰交战之事。而必曰交战之验乎。盖交战是人之通病。而至于此人则实以是成疾。故程子以此人之实病。验得交战之通病。而其曰验云者。犹曰證验云尔。若指交战之实。则下不得验字矣。如此看得则必不害心疾一句。实为此而发。文势语脉。相为贯通。退陶两条合一条之说。自是一时存疑之说。而似不可以是为定论。未知此说如何。
从验字上看得如此甚好。尝见刊补。亦以交战直作心疾看。
或问自欺曰心之发。不知不觉陷于自欺。(止。)为善以自欺也。此条可疑。自欺云者。固非阴有心于为恶。而若曰心之所发。不知不觉地见陷云尔。则所失者只在凌遽之间。不其大恕矣乎。(李在韶)
此条尝考语类本文。则恐篁墩节约得太过。尝见语类心发之下。有阳善阴恶四个字。不知不觉之上。有乃是见理不实六字。因其本语而味其语意。则心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1H 页
 发一句。非可以直接于不知不觉之上。而又于不知不觉之上。添了见理不实之意。然后语意方足。盖不知不觉字。连见理不实字而看之。则这个本不是卒乍间陷溺之意。亦不是全然无知觉之谓。其记录本语如此。而篁墩节约得太简。所以骤见不能无疑。
发一句。非可以直接于不知不觉之上。而又于不知不觉之上。添了见理不实之意。然后语意方足。盖不知不觉字。连见理不实字而看之。则这个本不是卒乍间陷溺之意。亦不是全然无知觉之谓。其记录本语如此。而篁墩节约得太简。所以骤见不能无疑。宁可逐些吃令饱为是乎。质疑则以为为己之学。用心于内。铢累寸积而有得也。考误则以为略知义理。自以谓尽知之意释之。窃谓以下文略从肚过之意观之。则考误说似胜。(在河)
芝山亦以下文略从肚里之意。赚看此句。故改释如此。然愚意则溪训似不可易。盖朱子之意。以逐些之吃摊门之饭设两端。以明虚实之分。而这里本无略知义理。自以为知底意。则芝山说恐误。
赵致道言恶几亦诚之动。动以诚则无妄。既无妄则安有恶几之动乎。溪训以朱子因天理而有人欲之说及程子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之说为證。然天理之有人欲。非天理中有此人欲。指其流而言也。性与理则因可以如此说。而若夫诚则异于是。岂可曰诚之动为恶几乎。(世鹤)
按通书本注。朱子以实理二字释诚字。又曰诚便是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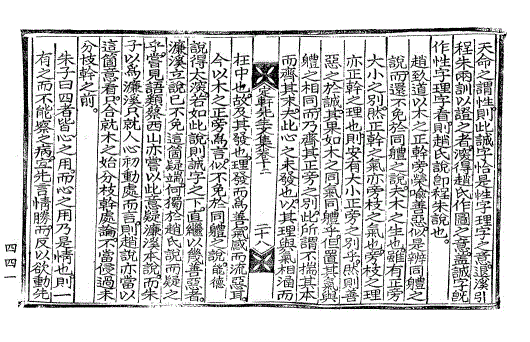 天命之谓性。则此诚字恰是性字理字之意。退溪引程朱两训以證之者。深得赵氏作图之意。盖诚字既作性字理字看。则赵氏说即程朱说也。
天命之谓性。则此诚字恰是性字理字之意。退溪引程朱两训以證之者。深得赵氏作图之意。盖诚字既作性字理字看。则赵氏说即程朱说也。赵致道以木之正干旁荣喻善恶。似是辨同体之说。而还不免于同体之说。夫木之生也。虽有正旁大小之别。然正干之气亦旁枝之气也。旁枝之理亦正干之理也。则安有大小正旁之别乎。然则善恶之于诚。其果如木之同气同体乎。但置其气与体之相同。而乃齐其正旁之别。此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夫此心之未发也。以其理与气相涵而在中也。故及其发也。理发而为善。气感而流恶耳。今以木之正旁为言。似不免于同体之说。(能德)
说得太深。若如此说则诚字之下。直继以几善恶者。濂溪立说已不免这个疑端。何独于赵氏说而疑之乎。尝见语类蔡西山亦尝以此意疑濂溪本说。而朱子以为濂溪只就人心初动处而言。则赵说亦当以这个意看。只合就木之始分枝干处论。不当侵过未分枝干之前。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心之用乃是情也。则一有之而不能察之病。宜先言情胜。而反以欲动先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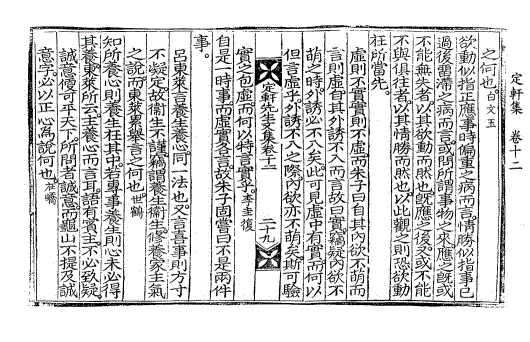 之何也。(白文玉)
之何也。(白文玉)欲动似指正应事时偏重之病而言。情胜似指事已过后留滞之病而言。或问所谓事物之来。应之既或不能无失者。以其欲动而然也。既应之后。又或不能不与俱往者。以其情胜而然也。以此观之则恐欲动在所当先。
虚则不实实则不虚。而朱子曰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则虚。自其外诱不入而言故曰实。窃疑内欲不萌之时。外诱必不入矣。此可见虚中有实。而何以但言虚乎。外诱不入之际。内欲亦不萌矣。斯可验实之包虚。而何以特言实乎。(李圭复)
自是一时事。而虚实各言。故朱子固尝曰不是两件事。
吕东莱言养生养心。同一法也。又言喜事则方寸不凝定。故卫生不谨。窃谓养生卫生。修养家主气之说。而东莱累举言之何也。(世鹤)
知所养心则养生在其中。若专事养生则心未必得其养。东莱所云。主养心而言耳。语有宾主。不必致疑。
诚意便可平天下。所问者诚意。而龟山不提及诚意字。必以正心为说何也。(在峤)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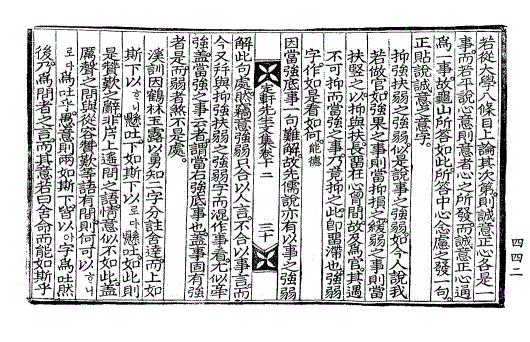 若从大学八条目上论其次第。则诚意正心各是一事。而若平说心意则意者心之所发。而诚意正心通为一事。故龟山所答如此。所答中心念虑之发一句。正贴说诚意之意字。
若从大学八条目上论其次第。则诚意正心各是一事。而若平说心意则意者心之所发。而诚意正心通为一事。故龟山所答如此。所答中心念虑之发一句。正贴说诚意之意字。抑强扶弱之强弱。似是说事之强弱。如今人说我若做官。如强果之事则当抑损之。缓弱之事则当扶竖之。以抑与扶。长留在心胸间。故及为官。其遇不可抑而当强之事。乃竟抑之。此即留滞也。强弱字。作如是看如何。(能德)
因当强底事一句难解。故先儒说亦有以事之强弱解此句处。然窃意强弱只合以人言。不合以事言。而今又并与抑强扶弱之强弱字而混作事看。尤似牵强。盖当强之事云者。谓当右强底事也。盖事固有强者是。而弱者煞不是处。
溪训因鹤林玉露以勇知二字分注舍达。而上如斯下以니悬吐。下如斯下以로다悬吐。如此则是赞叹之辞。非岸上遥问之语。情意似不如此。盖厉声之问与从容赞叹等语有间。则何可以니로다为吐乎。愚意则两如斯下。皆以아字为吐然后。乃为问者之言。而其意若曰舍命而能如斯乎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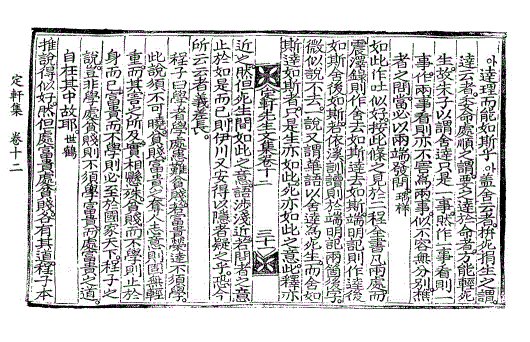 아达理而能如斯乎아盖舍云者。拚死捐生之谓。达云者。委命处顺之谓。要之达于命者。方能轻死生。故朱子以谓舍达只是一事。然作一事看则一事。作两事看则亦不害为两事。似不容无分别。樵者之问。当必以两端发问。(瑀祥)
아达理而能如斯乎아盖舍云者。拚死捐生之谓。达云者。委命处顺之谓。要之达于命者。方能轻死生。故朱子以谓舍达只是一事。然作一事看则一事。作两事看则亦不害为两事。似不容无分别。樵者之问。当必以两端发问。(瑀祥)如此作吐似好。按此条之见于二程全书凡两处。而震泽录则作舍去如斯达去如斯。端明记则作达后如斯舍后如斯。若依溪训读则于端明记两个后字。微似说不去。一说又谓华语以舍达为死生。而舍如斯达如斯者。只是生亦如此。死亦如此之意。此释亦近之。然但死生间如此之意。语涉浅近。若问者之意止于如是而已。则伊川又安得以隐者疑之乎。恐今所云云者义差长。
程子曰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不须学。此说须不可晓。贫贱富贵之夺人志意则固无轻重。而其害之所及。实相悬殊。贫贱而不学则止于身而已。富贵而不学则必至于国家天下。程子之说。岂非学处贫贱则不须学富贵。而处富贵之道。自在其中故耶。(世鹤)
推说得似好。然但处富贵处贫贱。各有其道。程子本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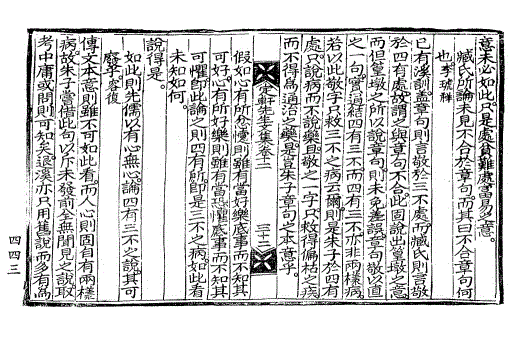 意未必如此。只是处贫难处富易之意。
意未必如此。只是处贫难处富易之意。臧氏所论未见不合于章句。而其曰不合章句何也。(李琥祥)
已有溪训。盖章句则言敬于三不处。而臧氏则言敬于四有处。故谓之与章句不合。此固说出篁墩之意。而但篁墩之所以说章句。则未免差误。章句敬以直之一句。实通结四有三不。而四有三不。亦非两样病。若以此敬字只救三不之病云尔。则是朱子于四有处。只说病而不说药。且敬之一字。只救得偏枯之疾。而不得为通治之药。是岂朱子章句之本意乎。
假如心有所忿懥则虽有当好乐底事而不知其可好。心有所好乐则虽有当恐惧底事而不知其可惧。即此论之则四有所。即是三不之病。如此看未知如何。
说得是。
如此则先儒以有心无心。论四有三不之说。其可废乎。(容复)
传文本意则虽不可如此看。而人心则固自有两样病。故朱子尝借此句以斥未发前全无闻见之说。取考中庸或问则可知矣。退溪亦只用旧说而多有为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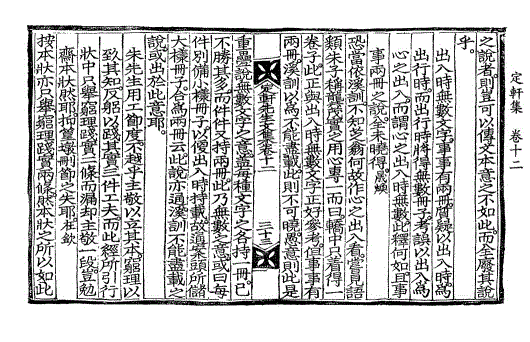 之说者。则岂可以传文本意之不如此。而全废其说乎。
之说者。则岂可以传文本意之不如此。而全废其说乎。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质疑以出入时。为出行时。而出行时将得无数册子。考误以出入为心之出入。而谓心之出入时无数。此释何如。且事事两册之说。全未晓得。(晟焕)
恐当依溪训。不知芝翁何故作心之出入看。尝见语类朱子称龚茂实之用心专一而曰。轿中只着得一卷子。此正与出入时无数文字正好参考。但事事有两册。溪训以为不能尽载。此则不可晓。愚意则此是重叠说无数文字之意。盖每种文字之各持一册。已不胜其多。而件件又持两册。此乃无数之意。或曰每件别备小样册子。以便出入时持载。故通案头所储大样册子。合为两册云。此说亦通。溪训不能尽载之说。或出于此意耶。
朱先生用工节度。不越乎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三件工夫。而此经所引行状中只举穷理践实二条而漏却主敬一段。岂勉斋本状然耶。抑篁墩删节之失耶。(在钦)
按本状亦只举穷理践实两条。然本状之所以如此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4L 页
 者。非略之也。其下即继之曰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云尔。则其归重于敬字之旨。反有胜于列书者矣。然则篁墩附注时决不当漏了此一句。而删节之不可晓。
者。非略之也。其下即继之曰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云尔。则其归重于敬字之旨。反有胜于列书者矣。然则篁墩附注时决不当漏了此一句。而删节之不可晓。廖晋卿读何书。朱子以九容处体认。待有意思。却好读书答之。而又继之以辨奸论。又终之以刘淳叟学道家打坐。上下文义。似不相续。(琥祥)
尝见语类。好读书以上则时举录。辨奸论以下则义刚录。今所行刊补中。已考得出矣。又刘淳叟之学道家打坐者。乃是收敛精神之错了路头处。与朱子所以语晋卿者论證不同。而篁墩乃合之。亦不可晓。
要好看却从外糊七字。旧无明释。今之读者多以从外之外。作窗外之外看。窃疑向明之窗。自有背腹。则从窗背糊纸。本无是理。亦安有好看之理。若如此说。则上不与朱子不齐整之说不相对值。下不与勉齐自欺说不甚衬贴。终觉可疑。(在镀)
外糊者。如今所谓面纸也。盖糊窗之好看。只在面纸一重。意当时糊窗者。于初一重糊涂时。有所不齐整。故朱夫子以便不是道理戒之。季绎之意以为入里底纵有些少不齐整处。固自无妨。而要好看则只在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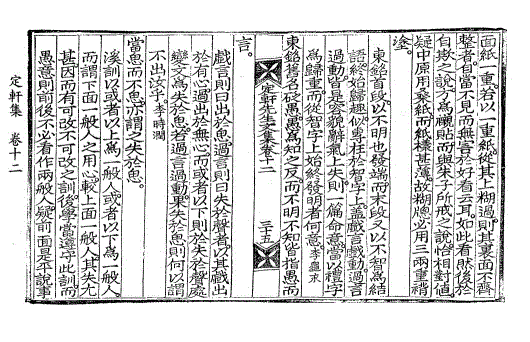 面纸一重。若以一重纸。从其上糊过。则其里面不齐整者。自当不见而无害于好看云耳。如此看然后于自欺之说。方为衬贴。而与朱子所戒之说。恰相对值。疑中原用桑纸。而纸样甚薄。故糊窗必用三两重褙涂。
面纸一重。若以一重纸。从其上糊过。则其里面不齐整者。自当不见而无害于好看云耳。如此看然后于自欺之说。方为衬贴。而与朱子所戒之说。恰相对值。疑中原用桑纸。而纸样甚薄。故糊窗必用三两重褙涂。东铭首段。以不明也发端。而末段又以不智为结语。终始归趣。似专在于智字上。盖戏言戏动。过言过动。皆是容貌辞气上失。则一篇命意。当以礼字为归重。而从智字上始终发明者何意。(李龟永)
东铭旧名砭愚。愚为知之反。而不明不知皆指愚而言。
戏言则曰出于思。过言则曰失于声者。以其戏出于有心。过出于无心。而或者以下则于失于声处变文为失于思。若过言过动。果失于思则何以谓不出汝乎。(李时润)
当思而不思。亦谓之失于思。
溪训以或者以上为一般人。或者以下为一般人。而谓下面一般人之用心。较上面一般人。其失尤甚。因而有可改不可改之训。后学当遵守此训。而愚意则前后不必看作两般人。疑前面是平说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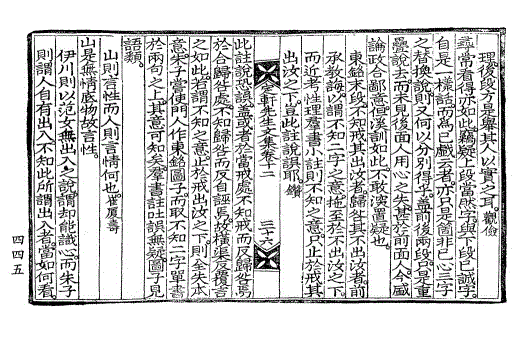 理。后段方是举其人以实之耳。(观俭)
理。后段方是举其人以实之耳。(观俭)寻常看得亦如此。窃疑上段当然字。与下段己诚字。自是一样话。而为己戏云者。亦只是个非己心三字之替换说。则又何以分别得乎。盖前后两段。只是重叠说去。而未见后面人用心之失。甚于前面人。今盛论政合鄙意。但溪训如此。不敢深置疑也。
东铭末段。不知戒其出汝者。归咎其不出汝者。前承教诲。以谓不知二字之意。拖至于不出汝之下。而近考性理群书小注则不知之意。只止于戒其出汝之下。岂此注说误耶。(钻)
此注说恐误。盖或者于当戒处不知戒而反归咎焉于合归咎处。不知归咎而反自诬焉。故横渠反覆言之如此。若谓不知之意。止于戒出汝之下。则全失本意。朱子尝使门人作东铭图子。而取不知二字单书于两句之上。其意可知矣。群书注吐误无疑。图子见语类。
山则言性而人则言情何也。(崔厦寿)
山是无情底物故言性。
伊川则以范女无出入之说。谓却能识心。而朱子则谓人自有出入。不知此所谓出入者。当如何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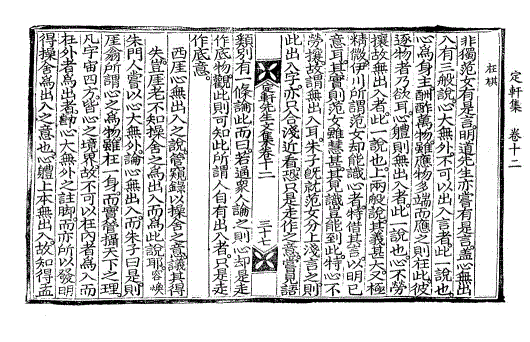 (在祺)
(在祺)非独范女有是言。明道先生亦尝有是言。盖心无出入有三般说。心大无外。不可以出入言者。此一说也。心为身主。酬酢万物。虽应物多端而应之则在此。彼逐物者乃欲耳。心体则无出入者。此一说也。心不劳攘故无出入者。此一说也。上两般说。其义甚大。又极精微。伊川所谓范女却能识心者。特借其言。以明己意耳。其实则范女虽慧甚。其见识岂能到此。特心不劳攘。故谓无出入耳。朱子既就范女分上浅言之。则此出入字。亦只合浅近看。恐只是走作之意。尝见语类别有一条论此而曰。若通众人论之则心却是走作底物。观此则可知此所谓人自有出入者。只是走作底意。
西厓心无出入之说。管窥录以操舍之意。议其得失。岂厓老不知操舍之为出入而为此说耶。(容焕)
朱门人尝以心大无外。论心无出入。而朱子曰是。则厓翁所谓心之为物。虽在一身。而实管摄天下之理。凡宇宙四方。皆心之境界。故不可以在内者为入而在外者为出者。即心大无外之注脚。而亦所以发明得操舍为出入之意也。心体上本无出入。故知得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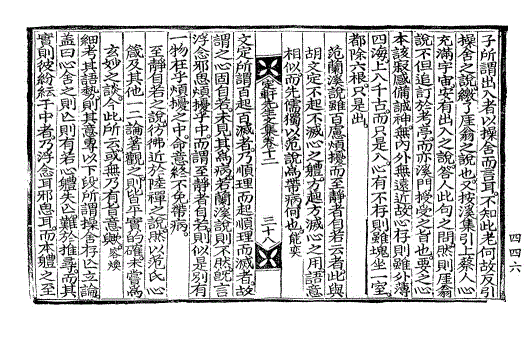 子所谓出入者以操舍而言耳。不知此老何故反引操舍之说。缴了厓翁之说也。又按溪集引上蔡人心充满宇宙。安有出入之说。答人此句之问。然则厓翁说不但追订于考亭。而亦溪门授受之旨也。要之心本该寂感备诚神。无内外无远近。故心存则虽外薄四海。上入千古。而只是入。心有不存则虽块坐一室。都除六根。只是出。
子所谓出入者以操舍而言耳。不知此老何故反引操舍之说。缴了厓翁之说也。又按溪集引上蔡人心充满宇宙。安有出入之说。答人此句之问。然则厓翁说不但追订于考亭。而亦溪门授受之旨也。要之心本该寂感备诚神。无内外无远近。故心存则虽外薄四海。上入千古。而只是入。心有不存则虽块坐一室。都除六根。只是出。范兰溪说虽百虑烦扰而至静者自若云者。此与胡文定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语意相似。而先儒独以范说为带病何也。(能奕)
文定所谓百起百灭者。乃顺理而起顺理而灭者。故谓之心固自若。未见其为病。若兰溪说则不然。既言浮念邪思烦扰乎中。而谓至静者自若。则似是别有一物在乎烦扰之中。命意终不免带病。
至静自若之说。彷佛近于陆禅之说。然以范氏心箴及其他一二论著观之。则皆平实的确。未尝为玄妙之谈。今此所云。或无乃有旨意欤。(容焕)
细考其语势。则其意专以下段所谓操舍存亡立论。盖曰心舍之则亡则有若心体失亡。难于推寻。而其实则彼纷纭于中者。乃浮念耳邪思耳。而本体之至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7H 页
 静则固自若。故人苟能知所以操之则当下便存。不费推寻云耳。其意似是如此。而特语势失先后。故骤看之则不能无病。
静则固自若。故人苟能知所以操之则当下便存。不费推寻云耳。其意似是如此。而特语势失先后。故骤看之则不能无病。朱子答石子重书。言操存一段。而以为正是直指心之体用云云。窃谓操舍存亡出入无时等语。谓之指心之用则可。而谓之指心之体则可疑。(在祺)
所操而存者。是即本体。岂可谓专说用。不及体耶。但朱子于此。虽谓直指心之体用。而若孔子本意则只是说人心得失之易保守之难。而不是本体上说。故朱子又尝曰这里不须说体。
前承教诲以上著床之床。为寝卧床。窃疑人之患多思虑者。虽未就卧床。未尝不纷纭。则张天祺之必就卧床然后。始为约不思虑之方何也。(任镇宰)
只为既就卧床则许多思虑。无放顿处故也。如思量处事而便做事不得。又如思量作文而便写纸不得。故只管辗转思量去。致人思虑上添思虑。此张天祺所以就卧床后。约不思虑者也。朱子尝论天祺此意甚详。就考语类则可知矣。又按刊补以此床通称坐卧床者。恐似失勘。此是卧床。不是坐床。
又曰人心作主不定云云。张天祺自上著床便不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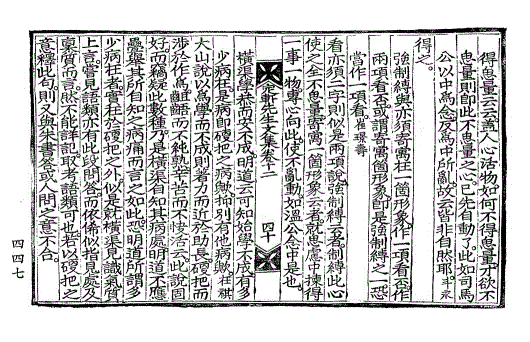 得思量云云。盖人心活物。如何不得思量。才欲不思量则即此不思量之心。已先自动了。此如司马公以中为念。反为中所乱。故云皆非自然耶。(斗永)
得思量云云。盖人心活物。如何不得思量。才欲不思量则即此不思量之心。已先自动了。此如司马公以中为念。反为中所乱。故云皆非自然耶。(斗永)得之。
强制缚与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作一项看否。作两项看否。或谓寄寓个形象。即是强制缚之一。恐当作一项看。(崔璟寿)
看亦须二字则似是两项说。强制缚云者。制缚此心使之全不思量。寄寓一个形象云者。就思虑中拣得一事一物。专心向此。使不乱动。如温公念中是也。
横渠学恭而安不成。明道云可知始学不成。有多少病在。是病即硬把之病欤。抑别有他病欤。(在祺)
大山说以为学而不成则著力而近于助长。硬把而涉于作为。龃龉而不纯熟。辛苦而不快活云。此说固好。而窃疑此数种。乃是横渠自知其病处。明道不应叠举其所自知之病痛而言之如此。恐明道所谓多少病在者。实在于硬把之外。似是就横渠见识气质上言。尝见语类亦有此段问答。而依俙似指见处及禀质而言。然不能详记。取考语类可也。若以硬把之意释此句。则又与朱书答或人问之意不合。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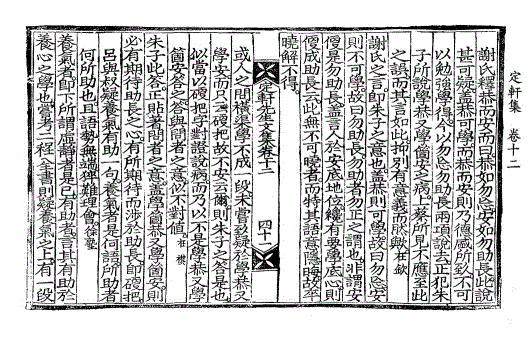 谢氏释恭而安而曰。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长。此说甚可疑。盖恭可学。而恭而安则乃德盛所致。不可以勉强学得。今以勿忘勿助长两项说去。正犯朱子所说学恭又学个安之病。上蔡所见不应至此之误。而其言如此。抑别有意义而然欤。(在钦)
谢氏释恭而安而曰。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长。此说甚可疑。盖恭可学。而恭而安则乃德盛所致。不可以勉强学得。今以勿忘勿助长两项说去。正犯朱子所说学恭又学个安之病。上蔡所见不应至此之误。而其言如此。抑别有意义而然欤。(在钦)谢氏之言。即朱子之意也。盖恭则可学。故曰勿忘。安则不可学。故曰勿助长。勿助者勿正之谓也。非谓安便是勿助长。盖言人于安底地位。才有要学底心。则便成助长云。此无不可晓者。而特其语意隐晦。故卒晓解不得。
或人之问横渠学不成一段。未尝致疑于学恭又学安。而只云硬把故不安云尔。则朱子之答是也。似当以硬把字对證说病。而乃以不是学恭又学个安答之。答与问者之意。似不对值。(在祺)
朱子此答。正贴著问者之意。盖学个恭又学个安。则必有期待助长之心。有所期待而涉于助长。即硬把。
吕与叔疑养气有助一句。养气者是何语。所助者何所助也。且语势无端。猝难理会。(徐塾)
养气者。即下所谓虚静者是已。有助者。言其有助于养心之学也。尝考二程全书则疑养气之上。有一段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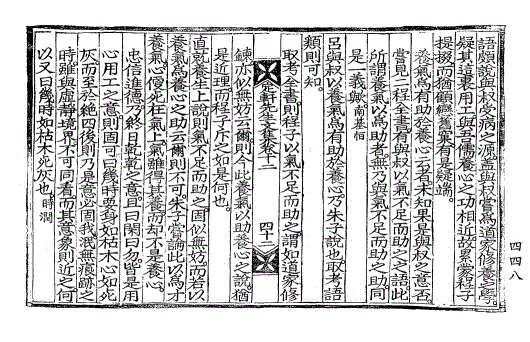 语颇说与叔受病之源。盖与叔尝为道家修养之学。疑其这里用工。与吾儒养心之功相近。故累蒙程子提掇。而犹顾恋旧窠。有是疑端。
语颇说与叔受病之源。盖与叔尝为道家修养之学。疑其这里用工。与吾儒养心之功相近。故累蒙程子提掇。而犹顾恋旧窠。有是疑端。养气为有助于养心云者。未知果是与叔之意否。尝见二程全书。有与叔以气不足而助之之语。此所谓养气以为助者。无乃与气不足而助之助。同是一义欤。(南基恒)
吕与叔以养气为有助于养心。乃朱子说也。取考语类则可知。
取考全书。则程子以气不足而助之。谓如道家修鍊。亦似无妨云尔。则今此养气以助养心之说。犹是近理。而程子斥之如是何也。
直就养生上说则气不足而助之。固似无妨。而若以养气为养心之助云尔则不可。朱子尝论此以为才养气。心便死在气上。气虽得其养。而却不是养心。
忠信进德。乃终日乾乾之意。且曰闲曰勿。皆是用心用工之意。则固可曰几时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而至于绝四后则乃是意必固我。泯无痕迹之时。虽与虚静境界。不可同看。而其意象则近之。何以又曰几时如枯木死灰也。(时润)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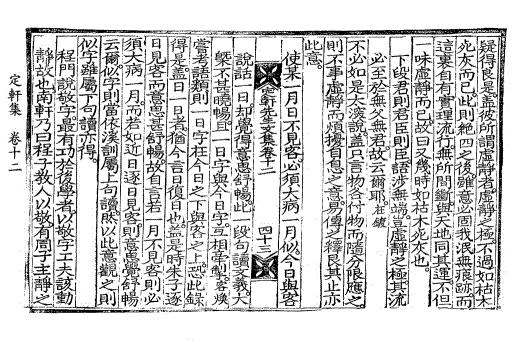 疑得良是。盖彼所谓虚静者。虚静之极。不过如枯木死灰而已。此则绝四之后。虽意必固我泯无痕迹。而这里自有实理流行。无所间断。与天地同其运。不但一味虚静而已。故曰又几时如枯木死灰也。
疑得良是。盖彼所谓虚静者。虚静之极。不过如枯木死灰而已。此则绝四之后。虽意必固我泯无痕迹。而这里自有实理流行。无所间断。与天地同其运。不但一味虚静而已。故曰又几时如枯木死灰也。下段君则君臣则臣。语涉无端。岂虚静之极。其流必至于无父无君。故云尔耶。(在镀)
不必如是太深说。盖只言物各付物而随分限应之。则不事虚静而烦扰自息之意。易传之释艮其止亦此意。
使某一月日不见客。必须大病一月似。今日与客说话一日。却觉得意思舒畅。此一段句读文义。大槩不甚晓畅。且一日字与今日字。互相牵掣。(容焕)
尝考语类则一日字在今日之下与客之上。恐此录得是。盖日一日者。犹今言日复日也。盖是时朱子逐日见客而意思甚舒畅。故自言若一月不见客则必须大病一月。而若如近日逐日见客。则意思觉舒畅云尔。似字则当依溪训属上句读。然以此意观之则似字虽属下句读亦得。
程门说敬字。最有功于后学者。以敬字工夫该动静故也。南轩乃曰程子教人以敬。有周子主静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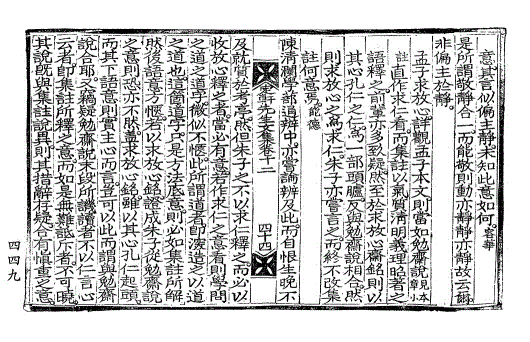 意。其言似偏主静。未知此意如何。(容华)
意。其言似偏主静。未知此意如何。(容华)是所谓敬静合一。而能敬则动亦静静亦静故云尔。非偏主于静。
孟子求放心。详观孟子本文。则当如勉斋说(见本章小注)直作求仁看。而集注以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之语释之。前辈亦多致疑。然至于求放心斋铭则以其心孔仁之仁。为一部头胪。反与勉斋说相合。然则求放心之为求仁。朱子亦尝言之。而终不改集注何意焉。(能德)
陈清澜学蔀通辨中。亦尝论辨及此。而自恨生晚不及就质于考亭。然但朱子之不以求仁释之。而必以收放心释之者。当必有意。若作求仁之意看则学问之道之道字。微似不惬。此所谓道者。即深造之以道之道也。这个道字。只是方法底意。则必如集注所解然后语意方惬。若以求放心铭。證成朱子从勉斋说之意则恐亦不然。盖求放心铭。虽以其心孔仁起头。而其下语意则实主心而言。岂可以此而谓与勉斋说合耶。又窃疑勉斋说末段所讥读者不以仁言心云者。即集注所释之意。而如是无难诋斥者。不可晓。其说既与集注说异。则其措辞存疑。合有慎重之意。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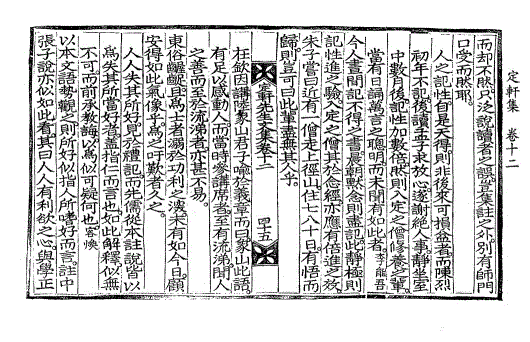 而却不然。只泛说读者之误。岂集注之外。别有师门口受而然耶。
而却不然。只泛说读者之误。岂集注之外。别有师门口受而然耶。人之记性。自是天得。则非后来可损益者。而陈烈初年不记。后读孟子求放心。遂谢绝人事。静坐室中数月后。记性加数倍。然则入定之僧修养之辈。当有日诵万言之聪明。而未闻有如此者。(李能吾)
今人昼间记不得之书。晨朝默念则尽记。此静极则记性进之验。入定之僧其于念经。亦应有倍进之效。朱子尝曰近有一僧走上径山。住七八十日。有悟而归。则岂可曰此辈尽无其人乎。
在钦因讲陆象山君子喻于义章而曰。象山此语。有足以感动人。而当时参讲席者。至有流涕。闻人之善而至于流涕者。亦甚不易。
东俗龌龊。且为士者溺于功利之深。未有如今日。顾安得如此气像乎。为之吁叹者久之。
人人失其所好。见于礼记。而先儒从本注说皆以为失其所当好者。盖指仁而言也。如此解释。似无不可。而前承教诲。以为似可疑何也。(容焕)
以本文语势观之。则所好似指人所嗜好而言。注中张子说亦似如此看。其曰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0L 页
 相背驰云者。即是这个意思。
相背驰云者。即是这个意思。四勿箴哲人。质疑则以哲人为圣人。考误则以为哲人虽心通理明而未及于圣人。若已是圣人则何至用功然后为圣人也云云。二说孰是。
圣人则不待诚于思而自无不中。窃意哲人恐似非指圣人而言。按语类朱子尝论此两句。而以为这是说两般人。又或问志士哲人优劣。朱子亦不苦分优劣。而但曰此只是说两种。又曰诚于思而不守于为不可。守于为而不诚于思亦不可云云。观此等语势。则朱子亦不将哲人作圣人看也明矣。若是圣人则语意必不如是。要之人自有这两般。一个则知能识微。一个则力能持守。故伊川只借此两般人。以明动字地面微著之分。尝见语类一处。又以哲人志士。谓非两般人。朱子既明言是两般。而又曰非两般者。盖见当时门人。亦只分人品优劣。而不从思为微著上看。故其说又如此。盖欲使人就一人心上作微著看。考误说虽得之。而亦似未及看得出程子本意。
此意盖有在一句。是门人释朱子之意否。抑朱子自言其意否。质疑以为门人说。而味其语意。似是朱子自言其意。未知当如何看。(黄瓒彬)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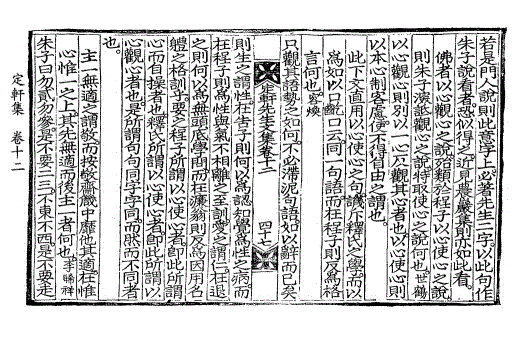 若是门人说则此意字上。必著先生二字。以此句作朱子说看者。恐似得之。近见农岩集则亦如此看。
若是门人说则此意字上。必著先生二字。以此句作朱子说看者。恐似得之。近见农岩集则亦如此看。佛者以心观心之说。殆类于程子以心使心之说。则朱子深诋观心之说。特取使心之说何也。(世鹤)
以心观心则别以一心反观其心者也。以心使心则以本心制客虑。使不得省由之谓也。
此下文直用以心使心之句。讥斥释氏之学。而以为如以口龁口云。同一句语。而在程子则反为格言何也。(容焕)
只观其语势之如何。不必滞泥句语。如以辞而已矣则生之谓性。在告子则何以为认知觉为性之病。而在程子则为性与气不相离之至训。爱之谓仁。在退之则何以为无头底学问。而在濂翁则反为因用名体之格训乎。要之程子所谓以心使心者。即此所谓心而自操者也。释氏所谓以心使心者。即此所谓以心观心者也。是所谓句句同字字同。而然而不同者也。
主一无适之谓敬。而按敬斋箴中靡他其适。在惟心惟一之上。其先无适而后主一者何也。(李睎祥)
朱子曰勿贰勿参。是不要二三。不东不西。是不要走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1L 页
 作。盖心不走作然后不二不三者。乃可得以言。其用工之次立言之序。自当如此。然若通言之则主一便是无适。无适即是主一。而不必分先后。
作。盖心不走作然后不二不三者。乃可得以言。其用工之次立言之序。自当如此。然若通言之则主一便是无适。无适即是主一。而不必分先后。惟以相之相字。作何意看。莫是防微谨独切问近思。交致其工之意否。抑助字之意否。(斗永)
恐当作助字之意看。然于韵不叶。必作交相之义看然后方与常字同作平声。旧释中交相之释。似是为此。然作助字看然后。方与全铭中文义合。盖此是求放心铭。故以操存省察之意为主。而以切问近思为夹助之工。要之语势有宾主之别。且考大全则相字下有之字。意益分晓。岂或古韵虽作助字意看。亦有平声读之例耶。(按古诗则平去声。多有互押处。)
答敬甫书。其间二字未知指何间而言。且与上文语势不甚连续可疑。(柔燮)
就考大全则者也之下。有世衰道微异端蜂起八字。此八字不当删去。而篁墩误加删节。故其间二字解不得。又有文不相续之疑。芝山考误。已考得出矣。
朱子答何叔京书曰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按朱子旧说就鸢鱼上说。今乃晓然之说。就看鸢鱼人上说。而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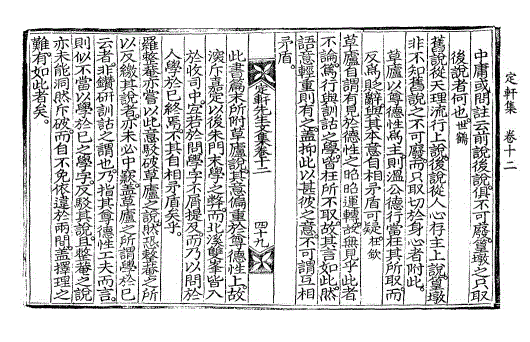 中庸或问注云前说后说。俱不可废。篁墩之只取后说者何也。(世鹤)
中庸或问注云前说后说。俱不可废。篁墩之只取后说者何也。(世鹤)旧说从天理流行上说。后说从人心存主上说。篁墩非不知旧说之不可废。而只取切于身心者附此。
草庐以尊德性为主。则温公德行当在其所取。而反为贬辞。与其本意自相矛盾可疑。(在钦)
草庐自谓有见于德性之昭昭运转。故无见乎此者不论。笃行与训诂之学。皆在所不取。故其言如此。然语意轻重则有之。盖抑此以甚彼之意。不可谓互相矛盾。
此书篇末所附草庐说。其意偏重于尊德性上。故深斥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北溪双峰皆入于收司中。宜若于问学字不屑提及。而乃以问于人学于己终焉。不其自相矛盾矣乎。
罗整庵亦尝以此意驳破草庐之说。然恐整庵之所以反缴其说者。亦未必中窾。盖草庐之所谓学于己云者。非钻研训诂之谓也。乃指其尊德性工夫而言。则似不当以学于己之学字。反驳其说。且整庵之说亦未能洞然斥破。而自不免依违于两间。盖择理之难。有如此者矣。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2L 页
 篁墩事实。退溪因皇明通纪中三条。反复论辨。尽其曲折。而窃独念篁墩童年名闻。词华彪发。白首穷经。多士宗仰。及其一考试券则辄有卖题之谤。才出名途则便招势利之诮。可疑。退溪于其卖题之谤。虽以理料度。知其必不然。而其事实真赝则未见有分明道破处。岂或更有可考之处耶。(厦寿)
篁墩事实。退溪因皇明通纪中三条。反复论辨。尽其曲折。而窃独念篁墩童年名闻。词华彪发。白首穷经。多士宗仰。及其一考试券则辄有卖题之谤。才出名途则便招势利之诮。可疑。退溪于其卖题之谤。虽以理料度。知其必不然。而其事实真赝则未见有分明道破处。岂或更有可考之处耶。(厦寿)程篁墩事迹。颇详于今所行刊补中。而但于卖题之事。不甚消详。只言华昂等之语塞反坐。而不言谗者执言之所以然。尝见明史则篁墩与学者唐寅等讲学。因语及科场可合之题。后数年篁墩掌试。寅等因呈宿构。及昂等弹章起。上命李东阳更阅篁墩考券。而寅等则初不与试。此卖题之谤所由起。而至于势利之诮。则疑篁墩为李贤婿。而贤柄政久。岂篁墩出入其门。故不悦者从而媒孽之欤。明人论篁墩行处。而断之以防世之疏。要之此四字。断尽此老平生。而云云之说则冤矣。岂其学术出入陆学。而于义理微密处。不屑用意。故有此疏旷之失欤。
今此问答。只是句读离绝及零琐文义而已。退陶先生所谓一生行不尽一生知不尽者。岂是之谓哉。学者所体验而受用者。正在于不费思索不费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3H 页
 讲说处。如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八字。人孰不知。亦岂有难知之奥义哉。一日用力则有一日之功。二日用力则有二日之功。而特人自不加之意耳。顾此颟顸。少而读是书。老不加工。至今白首纷如。都不得些子力。而并与区区诵读之功而全然放废。今因是会。重加温绎。而又因佥贤互相发难。多有发得新意处。此非问者之幸。乃答者之幸也。但口舌所腾之理。随问即对。而如是劄录。深恐碍人正知见。误人真眼目。而又将有转浼处。尤不胜愧忸。要之此辈人言语。被人抄录。已极可笑。而又从渠手中删繁汰蔓。极知其不韪。然但录者于多人发问之际。一边参听。一边记录。故其记录之辞。往往有失其语脉处。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于问者之情。亦有未尽其蕴者。是为可吝也。故不揆事面。删润如右。览者其尚恕之哉。
讲说处。如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八字。人孰不知。亦岂有难知之奥义哉。一日用力则有一日之功。二日用力则有二日之功。而特人自不加之意耳。顾此颟顸。少而读是书。老不加工。至今白首纷如。都不得些子力。而并与区区诵读之功而全然放废。今因是会。重加温绎。而又因佥贤互相发难。多有发得新意处。此非问者之幸。乃答者之幸也。但口舌所腾之理。随问即对。而如是劄录。深恐碍人正知见。误人真眼目。而又将有转浼处。尤不胜愧忸。要之此辈人言语。被人抄录。已极可笑。而又从渠手中删繁汰蔓。极知其不韪。然但录者于多人发问之际。一边参听。一边记录。故其记录之辞。往往有失其语脉处。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于问者之情。亦有未尽其蕴者。是为可吝也。故不揆事面。删润如右。览者其尚恕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