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杂著
杂著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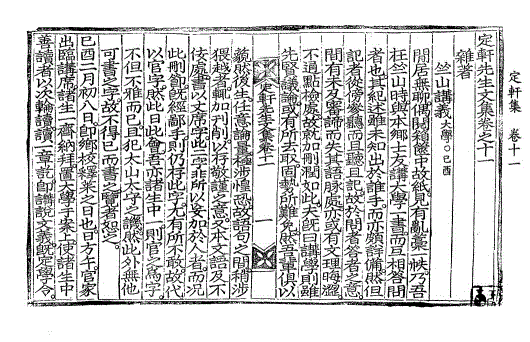 竺山讲义(大学○己酉)
竺山讲义(大学○己酉)閒居无聊。偶阅箱箧中故纸。见有乱藁一帙。乃吾在竺山时。与本乡士友讲大学一书。而互相答问者也。其纪述虽未知出于谁手。而亦颇详备。然但记者从傍参听而且听且记。故于问者答者之意。间有未及审谛而失其语脉处。亦或有文理晦涩。不通点检处。故就加删润如此。夫既曰讲学则虽先贤议论。或有所去取。固势所难免。然吾辈俱以藐然后生。任意论量。极涉惶恐。故语句之间。稍涉猥越者。辄加刊削。以存敬谨之意。又本文语及不佞处。书以丈席字。此二字非所以妄加于人者。而况此删节。既经鄙手。则仍存此字。尤有所不敢。故代以官字。然此日此会。吾亦诸生中一。则官之为字。不但不雅而已。且犯太山太守之讥。然此外无他可书之字。故不得已而书之。览者恕之。
己酉二月初八日。即乡校释菜之日也。日方午。官家出临讲席。诸生一齐纳拜。置大学于案上。使诸生中善读者以次轮读。读一章讫。即讲说文义。既定学令。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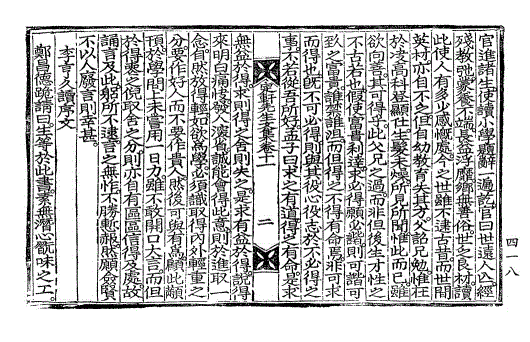 官进诸生。使读小学题辞一遍讫。官曰世远人亡。经残教弛。蒙养不端。长益浮靡。乡无善俗。世乏良材。读此使人有多少感慨处。今之世虽不逮古昔。而世间英材。亦自不乏。但自幼教育失其方。父诏兄勉。惟在于决高科登显仕。生发未燥。所见所闻。惟此而已。虽欲向善。其可得乎。此父兄之过。而非但后生才性之不古若也。假使富贵利达。求必得愿必谐。则可谐可致之富贵。谁禁谁沮。而但得之不得有命焉。非可求而得也。既不可必得。则与其役心役志于不必得之事。不若从吾所好。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说得来明白痛快。发人深省。诚能会得此意。则于进取一念。自然放得轻。如欲为学。必须识取得内外轻重之分。要作好人而不要作贵人。然后可与有为。顾此颟顸。于学问上未尝用一日力。虽不敢开口大言。而但于得丧之倪取舍之分。则亦自有区区信得及处。故诵言及此。躬所不逮。言之无怍。不胜惭赧。然愿佥贤不以人废言则幸甚。
官进诸生。使读小学题辞一遍讫。官曰世远人亡。经残教弛。蒙养不端。长益浮靡。乡无善俗。世乏良材。读此使人有多少感慨处。今之世虽不逮古昔。而世间英材。亦自不乏。但自幼教育失其方。父诏兄勉。惟在于决高科登显仕。生发未燥。所见所闻。惟此而已。虽欲向善。其可得乎。此父兄之过。而非但后生才性之不古若也。假使富贵利达。求必得愿必谐。则可谐可致之富贵。谁禁谁沮。而但得之不得有命焉。非可求而得也。既不可必得。则与其役心役志于不必得之事。不若从吾所好。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说得来明白痛快。发人深省。诚能会得此意。则于进取一念。自然放得轻。如欲为学。必须识取得内外轻重之分。要作好人而不要作贵人。然后可与有为。顾此颟顸。于学问上未尝用一日力。虽不敢开口大言。而但于得丧之倪取舍之分。则亦自有区区信得及处。故诵言及此。躬所不逮。言之无怍。不胜惭赧。然愿佥贤不以人废言则幸甚。李亨久读序文
郑昌德跪请曰。生等于此书。素无潜心玩味之工。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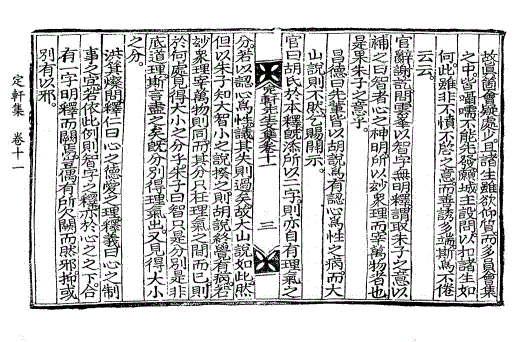 故真个会疑处少。且诸生虽欲仰质。而多员会集之中。皆嗫嚅不能先发。愿城主设问。以扣诸生如何。此虽非不愤不启之意。而善诱多端。斯为不倦云云。
故真个会疑处少。且诸生虽欲仰质。而多员会集之中。皆嗫嚅不能先发。愿城主设问。以扣诸生如何。此虽非不愤不启之意。而善诱多端。斯为不倦云云。官辞谢讫。问云峰以智字无明释。谓取朱子之意以补之曰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是果朱子之意乎。
昌德曰先辈皆以胡说为有认心为性之病。而大山说则不然。乞赐开示。
官曰胡氏于本释。既添所以二字。则亦自有理气之分。若以认心为性。议其失则过矣。故大山说如此。然但以朱子知大智小之说揆之。则胡说终觉有病。若妙众理宰万物则同。而其分只在理气之间而已。则于何处见得大小之分乎。朱子曰智只是分别是非底道理。斯言尽之矣。既分别得理气出。又见得大小之分。
洪箕灿问。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释义曰心之制事之宜。若依此例则智字之释。亦于心之之下。合有一字明释而阙焉。岂偶有所欠阙而然邪。抑或别有以邪。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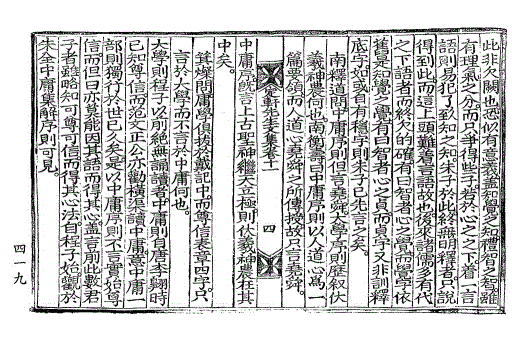 此非欠阙也。恐似有意义。盖知觉之知。礼智之智。虽有理气之分。而只争得些子。若于心之之下。着一言语则易犯了致知之知。朱子于此。终无明释者。只说得到此。而这上头难着言语故也。后来诸儒多有代之下语者而终欠的确。有曰智者心之觉。而觉字依旧是知觉之觉。有曰智者心之贞。而贞字又非训释底字。如或自有稳字则朱子已先言之矣。
此非欠阙也。恐似有意义。盖知觉之知。礼智之智。虽有理气之分。而只争得些子。若于心之之下。着一言语则易犯了致知之知。朱子于此。终无明释者。只说得到此。而这上头难着言语故也。后来诸儒多有代之下语者而终欠的确。有曰智者心之觉。而觉字依旧是知觉之觉。有曰智者心之贞。而贞字又非训释底字。如或自有稳字则朱子已先言之矣。南释道问。中庸序则但言尧舜。大学序则历叙伏羲神农何也。南衡寿曰中庸序则以人道心为一篇要领。而人道心尧舜之所传授。故只言尧舜。
中庸序。既言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则伏羲神农在其中矣。
箕灿问。庸学俱拔于戴记中。而尊信表章四字。只言于大学而不言于中庸何也。
大学则程子以前绝无诵读者。中庸则自唐李翱时已知尊信。而范文正公亦劝横渠读中庸。意中庸一部则独行于世已久矣。是以中庸序则不言实始尊信。而但曰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盖言前此数君子者虽略知可尊可信。而得其心法。自程子始。观于朱全中庸集解序则可见。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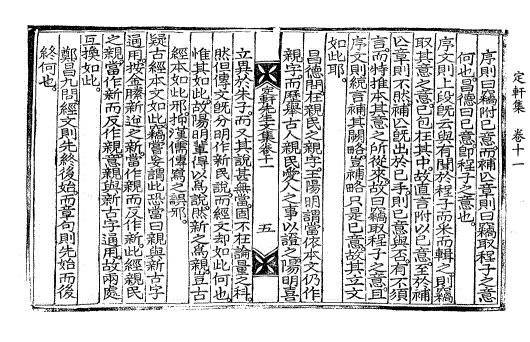 序则曰窃附己意。而补亡章则曰窃取程子之意何也。昌德曰己意。即程子之意也。
序则曰窃附己意。而补亡章则曰窃取程子之意何也。昌德曰己意。即程子之意也。序文则上段既云与有闻于程子而采而辑之。则窃取其意之意。已包在其中。故直言附以己意。至于补亡章则不然。补亡既出于己手。则己意与否。有不须言。而特推本其意之所从来。故曰窃取程子之意。且序文则统言补其阙略。岂补略只是己意。故其立文如此耶。
昌德问。在亲民之亲字。王阳明谓当依本文仍作亲字。而历举古人亲民爱人之事以證之。阳明喜立异于朱子。而又其说甚无当。固不在论量之科。然但传文既分明作新民说。而经文却如此何也。惟其如此。故阳明辈得以为说。然新之为亲。岂古经本如此邪。抑汉儒传写之误邪。
疑古经本文如此。窃尝妄谓此恐当曰亲与新古字通用。按金縢新逆之新。当作亲而反作新。此经亲民之亲。当作新而反作亲。意亲与新古字通用。故两处互换如此。
郑昌九问。经文则先终后始。而章句则先始而后终何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0L 页
 物以本为重。事以终为贵。故经文则先终而后始。然章句则本始末终。各以类释。故先始后终。别无深意。
物以本为重。事以终为贵。故经文则先终而后始。然章句则本始末终。各以类释。故先始后终。别无深意。格物之物字上。若依上例则亦当有其字。而只曰格物何也。
家国身心意知皆属其人分上。故着其字。至如事物之物则着其字不得。盖盈于天地间者皆是物也。而元不属其人分上。要之国也也是私。家也也是私。心与意知皆属于一己之私。而独物之理则散在天下万物。非我所得以私者。故立文如此。
李在祺问。朱子以为上项六条。皆有等级。到格物致知处便亲切。故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诚正修岂非亲切工夫。而独以格致为亲切者何也。
亲切云者。非谓格致工夫比诚正修最为亲切也。谓致知之与格物最相亲切。盖诚意之于致知。正心之于诚意。修身之于正心。未始不亲切。终是各有地头。各有工夫。至于致知格物则相离不得。致知便在格物上。而格物之外更无他致知工夫。故曰到格致处便亲切。
李畴九问。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云云。此章既说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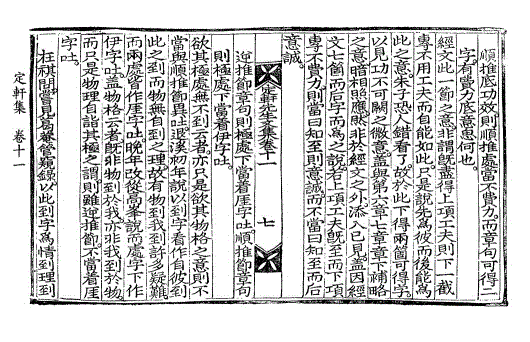 顺推底功效。则顺推处当不费力。而章句可得二字。有费力底意思何也。
顺推底功效。则顺推处当不费力。而章句可得二字。有费力底意思何也。经文此一节之意。非谓既尽得上项工夫则下一截专不用工夫而自能如此。只是说先为彼而后能为此之意。朱子恐人错看了。故于此下得两个可得字。以见功不可阙之微意。盖与第六章七章章下补略之意。暗相照应。然非于经文之外。添入己见。盖因经文七个而后字而为之说。若上项工夫既至而下项专不费力。则当曰知至则意诚。而不当曰知至而后意诚。
逆推节章句则极处下当着厓字吐。顺推节章句则极处下当着伊字吐。
欲其极处无不到云者。亦只是欲其物格之意则不当与顺推节异吐。退溪初年说以到字看作自彼到此之到而物无自到之理。故有物到我到许多疑难。而两处皆作厓字吐。晚年改从高峰说而处字下作伊字吐。盖物格云者。既非物到于我。亦非我到于物。而只是物理自诣其极之谓。则虽逆推节。不当着厓字吐。
在祺问。尝见葛庵管窥录。以此到字为情到理到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1L 页
 造得到之到。而以敬堂物理尽之释。为最得朱子之意。退溪晚年及高峰栗谷说。虽皆主理到之说。而其的确精当则恐敬堂尽字之释最胜。
造得到之到。而以敬堂物理尽之释。为最得朱子之意。退溪晚年及高峰栗谷说。虽皆主理到之说。而其的确精当则恐敬堂尽字之释最胜。此说虽似的确。而字义恐似不协。葛翁之意欲明理自诣极之意。故以敬堂说为最得朱子之意。然窃恐到字祗当作到字看。不必作尽字看。盖到字本格字替换底字。而格之为字。固是极至之义。然须是有个人能诣能至然后方名之格。如格于文祖之格苗民来格之格是已。是故朱子于此。不曰极处无不尽。而必曰无不到。至以或问观之。其释物格也亦不直曰物之理极尽无馀。而必曰诣其极。则其意可见。近世先辈以理本无情意无造作。而到字是有情意底字。故必看作尽字而后已。然以章句到字或问诣字互相参验。则到字恐祗当作到字看。且到与尽。合有分别。致知是全体说而从全体上渐次推广去。故曰尽。格物是零细说而从零细处各诣其极故曰到。
物理尽之说。非敬堂说也。程子所谓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即其说也。且语类亦有究极物理。使无不尽之说。恐不必如是分析。
格便是尽底意。至即是到底意。而朱子必以到字释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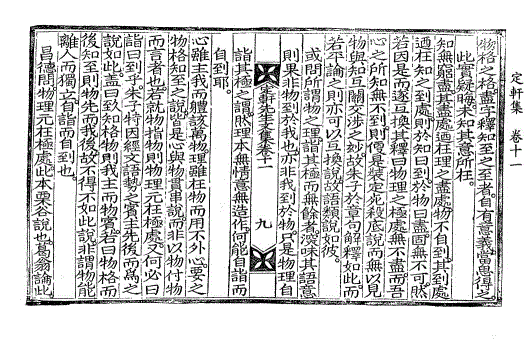 物格之格。尽字释知至之至者。自有意义。当思得之。
物格之格。尽字释知至之至者。自有意义。当思得之。此实疑晦。未知其意所在。
知无穷尽。其尽处乃在理之尽处。物不自到。其到处乃在知之到处。则于知曰到。于物曰尽。固无不可。然若因是而遂互换其释曰物理之极处无不尽。而吾心之所知无不到。则便是装定死杀底说而无以见物与知互关交涉之妙。故朱子于章句解释如此。而若平论之则亦可以互换说。故语类说如彼。
或问所谓物之理。诣其极而无馀者。深味其语意则果非物到于我也。亦非我到于物。只是物理自诣其极之谓。然理本无情意无造作。何能自诣而自到耶。
心虽主我而体该万物。理虽在物而用不外心。要之物格知至之说。皆是心与物贯串说。而非以物付物而言者也。若就物指物则物理元在极处。又何必曰诣曰到乎。朱子特因经文语势之宾主先后而为之说如此。盖曰致知格物则我主而物宾。若曰物格而后知至则物先而我后。故不得不如此说。非谓物能离人而独立。自诣而自到也。
昌德问。物理元在极处。此本栗谷说也。葛翁论此。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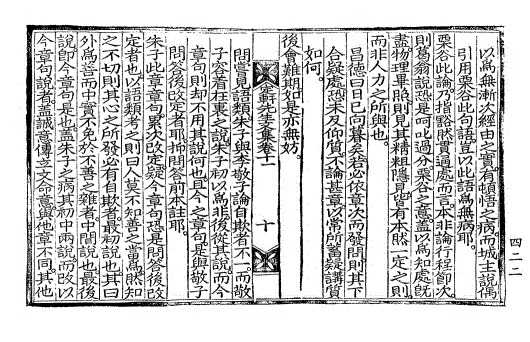 以为无渐次经由之实。有顿悟之病。而城主说偶引用栗谷此句语。岂以此语为无病耶。
以为无渐次经由之实。有顿悟之病。而城主说偶引用栗谷此句语。岂以此语为无病耶。栗谷此论。乃指豁然贯通处而言。本非论行程节次。则葛翁说恐是呵叱过分。栗谷之意。盖以为知处既尽。物理毕照。则见其精粗隐见。皆有本然一定之则。而非人力之所与也。
昌德曰日已向暮矣。若必依章次而发问。则其下合疑处。恐未及仰质。不论甚章。以常所蓄疑讲质如何。
后会难期。如是亦无妨。
问尝见语类。朱子与李敬子论自欺者不一。而敬子容着在里之说。朱子初以为非。后从其说。而今章句则却不用其说何也。且今之章句。是与敬子问答后改定者耶。抑问答前本注耶。
朱子此章章句。累次改定。疑今章句恐是问答后改定者也。以语类考之则曰人莫不知善之当为。然知之不切则其心之所发必有自欺者。最初说也。其曰外为善而中实不免于不善之杂者。中间说也。最后说。即今章句是也。盖朱子之病其初中两说。而改以今章句说者。盖诚意传立文命意。与他章不同。其他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3H 页
 诸章则不能修身者病在于心。不能齐家者病在于身。而若诚意章主意则与此异。乃为知己至而意或不诚者设此。所以别立诚意传者也。若依初说则是重在于知而不在于意。故改定为中说。然其曰不免云者。终始归重于知底意思胜。而不专说自欺工夫地头。此敬子所以疑而问也。细考其问答次第。则敬子之初。以中间说谓不如初说者。固是失问。而后次问答所谓不善之杂。非是不知。只是知得了。便是容着在里云者。则实是会得底语。盖自欺之欺。便是承接致知之知字。若全然不识不知则岂可谓之自欺乎。惟其能知善恶之所在而意有不诚者。是谓自欺耳。盖充其已致之知则纤毫恶念。无容着之地。而其所以容着在里者。以其自欺其本心之知故也。其说最说得自欺地头出来。章句虽不用敬子容着之说。而其大意则实与敬子说相近。先辈或以此章问答。谓在章句已定之后。而又以为语意不相合。然以愚考之则章句似因此章问答而改定者。而其语势意义。未见其不相合。
诸章则不能修身者病在于心。不能齐家者病在于身。而若诚意章主意则与此异。乃为知己至而意或不诚者设此。所以别立诚意传者也。若依初说则是重在于知而不在于意。故改定为中说。然其曰不免云者。终始归重于知底意思胜。而不专说自欺工夫地头。此敬子所以疑而问也。细考其问答次第。则敬子之初。以中间说谓不如初说者。固是失问。而后次问答所谓不善之杂。非是不知。只是知得了。便是容着在里云者。则实是会得底语。盖自欺之欺。便是承接致知之知字。若全然不识不知则岂可谓之自欺乎。惟其能知善恶之所在而意有不诚者。是谓自欺耳。盖充其已致之知则纤毫恶念。无容着之地。而其所以容着在里者。以其自欺其本心之知故也。其说最说得自欺地头出来。章句虽不用敬子容着之说。而其大意则实与敬子说相近。先辈或以此章问答。谓在章句已定之后。而又以为语意不相合。然以愚考之则章句似因此章问答而改定者。而其语势意义。未见其不相合。正心章四有所之有字。古今诸家皆看作留滞不化之意。而今之见行谚解。亦主是释。然若此个有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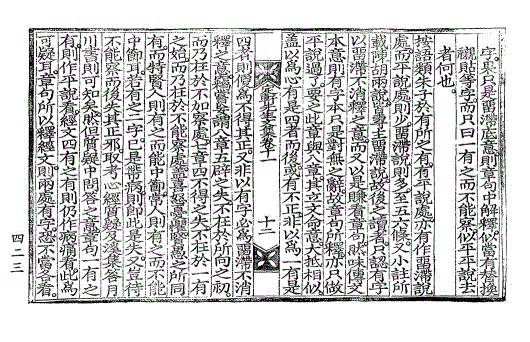 字。果只是留滞底意。则章句中解释。似当有替换衬贴等字。而只曰一有之而不能察。似平平说去者何也。
字。果只是留滞底意。则章句中解释。似当有替换衬贴等字。而只曰一有之而不能察。似平平说去者何也。按语类朱子于有所之有。有平说处。亦有作留滞说处。而平说处则少。留滞说则多。至五六条。又小注所载陈胡两说。皆专主留滞说。故后之读者。只认有字以留滞不消释之意。而又以是赚看章句。然味传文本意则有字本只是对无之辞。故章句所释。亦只做平说过了。要之此章与八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盖以为心有是四者而后。或有不正。非以为一有是四者则便为不得其正。又非以有字必为留滞不消释之意。窃尝妄谓八章五辟之失。不在于所向之初。而乃在于不加察处。七章四不得之失。不在于一有之始。而乃在于不能察处。盖喜怒忧惧。贤愚之所同有。而特贤人则有之而能中节。常人则有之而不能中节耳。若有之二字。已是带病。则即此是失。又岂待不能察而后失其正邪。取考心经质疑及溪集答月川书则可知矣。然但质疑中问答之意。章句一有之有。则作平说看。经文四有之有则仍作病痛看。此为可疑耳。章句所以释经文。则两处有字。恐不当各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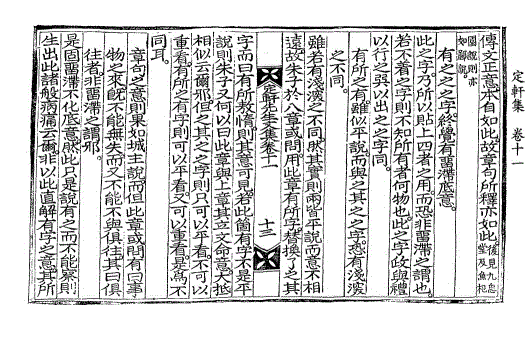 传文正意。本自如此。故章句所释亦如此。(后见九思堂及鱼杞园说则亦如鄙说。)
传文正意。本自如此。故章句所释亦如此。(后见九思堂及鱼杞园说则亦如鄙说。)有之之之字。终觉有留滞底意。
此之字。乃所以贴上四者之用。而恐非留滞之谓也。若不着之字则不知所有者何物也。此之字政与礼以行之巽以出之之字同。
有所之有。虽似平说。而与之其之之字。恐有浅深之不同。
虽若有浅深之不同。然其实则两皆平说而意不相远。故朱子于八章或问。用此章有所字。替换了之其字而曰有所敖惰。则其意可见。若此个有字不是平说则朱子又何以曰此章与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云尔邪。但之其之之字则只可以平看。不可以重看。有所之有字则可以平看。又可以重看。是为不同耳。
章句之意则果如城主说。而但此章或问有曰事物之来。既不能无失。而又不能不与俱往。其曰俱往者。非留滞之谓邪。
是固留滞不化底意。然此只是说有之而不能察则生出此诸般病痛云尔。非以此直解有字之意。其所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4L 页
 谓事物之来。或不能无失者。即语类所谓正应事时。意有偏重者也。其所谓又不能不与俱往者。即语类所谓事已过后长留滞之谓也。此外又有先事期待等病痛。若以有所之有。专做留滞说则包不得诸般病痛。故语类诸说虽往往只作留滞说。而于本章章句正解释处则只平说有字。而其下乃以欲动情胜四字继之。盖泛言欲动情胜则偏重留滞期待等诸般病痛。尽举之矣。章句之周遍精切攧扑不破。有如此者。
谓事物之来。或不能无失者。即语类所谓正应事时。意有偏重者也。其所谓又不能不与俱往者。即语类所谓事已过后长留滞之谓也。此外又有先事期待等病痛。若以有所之有。专做留滞说则包不得诸般病痛。故语类诸说虽往往只作留滞说。而于本章章句正解释处则只平说有字。而其下乃以欲动情胜四字继之。盖泛言欲动情胜则偏重留滞期待等诸般病痛。尽举之矣。章句之周遍精切攧扑不破。有如此者。欲动情胜则已失其正。岂有或不得其正者。沙栗诸贤皆以或字为疑。近闻有金农岩说最好而未及见。然或之一字。果不无疑晦之端。
农岩说。某曾年亦尝电披。而今不能尽记。然其大意则以为或不能无失一句。上应心之用人所不能无。而不系于欲动情胜。盖是四者。本无不正。而或不能不失者。以其有之而不能察。以至于欲动情胜而然耳。此说得之矣。而第未知农岩看得一有之有字何如耳。若有字不做平说看而豫做病痛看。则语意终觉阙促。退陶先生所谓只径说得不察。而不得其正者一边。更不容能察而得其正者占得地步云者。此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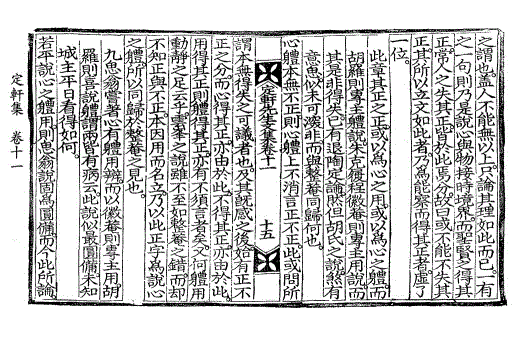 之谓也。盖人不能无以上。只论其理如此而已。一有之一句则乃是说心与物接时境界。而圣贤之得其正。常人之失其正。皆于此焉分。故曰或不能不失其正。其所以立文如此者。乃为能察而得其正者。虚了一位。
之谓也。盖人不能无以上。只论其理如此而已。一有之一句则乃是说心与物接时境界。而圣贤之得其正。常人之失其正。皆于此焉分。故曰或不能不失其正。其所以立文如此者。乃为能察而得其正者。虚了一位。此章其正之正。或以为心之用。或以为心之体。而胡罗则专主体说。朱克履程徽庵则专主用说。而其是非得失。已有退陶定论。然但胡氏之说。煞有意思。似未可深非。而与整庵同归何也。
心体本无不正。则心体上不消言正不正。此或问所谓本无得失之可议者也。及其既感之后。始有正不正之分。而心得其正。亦由于此。不得其正。亦由于此。用得其正则体得其正。亦有不须言者矣。又何体用动静之足云乎。云峰之说虽不至如整庵之错。而却不知正与不正。本因用而名立。乃以此正字为说心之体。所以同归于整庵之见也。
九思翁尝著心有体用辨。而以徽庵则专主用。胡罗则喜说体。谓两皆有病云。此说似最圆备。未知城主平日看得如何。
若平说心之体用。则思翁说固为圆备。而今此所论。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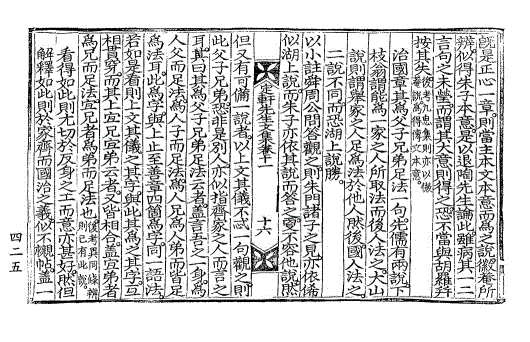 既是正心一章。则当主本文本意而为之说。徽庵所辨。似得朱子本意。是以退陶先生论此。虽病其一二言句之未莹。而谓其大意则得之。恐不当与胡罗并按其失。(后考九思集则亦以徽庵说。为得传文本意。)
既是正心一章。则当主本文本意而为之说。徽庵所辨。似得朱子本意。是以退陶先生论此。虽病其一二言句之未莹。而谓其大意则得之。恐不当与胡罗并按其失。(后考九思集则亦以徽庵说。为得传文本意。)治国章其为父子兄弟足法一句。先儒有两说。下枝翁谓能为一家之人所取法而后人法之。大山说则谓举家之人足为法于他人然后。国人法之。二说不同。而恐湖上说胜。
以小注舜周公问答观之。则朱门诸子之见。亦依俙似湖上说。而朱子亦依其说而答之。更不容他说。然但又有可备一说者。以上文其仪不忒一句观之。则此父子兄弟。恐非是别人。亦似指齐家之人而言之耳。其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云者。盖言吾之一身。为人父而足法。为人子而足法。为人兄为人弟而皆足为法耳。此为字。与上止至善章四个为字。同一语法。若如是看则上文其仪之其字。与此其为之其字。互相贯穿。而其上宜兄宜弟云者。又皆相合。盖宜弟者为兄而足法。宜兄者为弟而足法也。(后考异同条辨则已有此说。)
看得如此则尤切于反身之工而意亦甚好。然但解释如此则于家齐而国治之义。似不衬帖。盖一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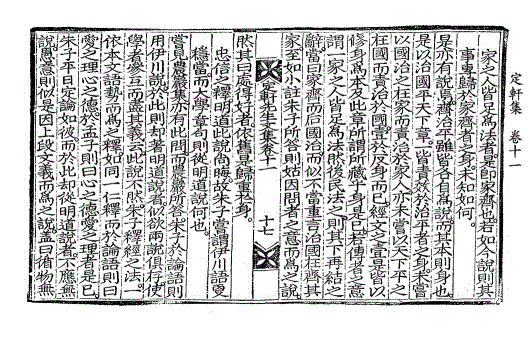 家之人皆足为法者。是即家齐也。若如今说则其事专归于家齐者之身。未知如何。
家之人皆足为法者。是即家齐也。若如今说则其事专归于家齐者之身。未知如何。是亦有说焉。齐治平虽皆各自为说。而其本则身也。是以治国平天下章。一皆责效于治平者之身。未尝以国治之在家而责治于家人。亦未尝以天下平之在国而责治于国。壹于反身而已。经文之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及此章所谓所藏乎身是已。若传者之意谓一家之人皆足为法然后民法之。则其下再结之辞。当曰家齐而后国治。而似不当重言治国在齐其家。至如小注朱子所答则姑因问者之意而为之说。然其曰处得好者。依旧是归重于身。
忠信之释。明道此说尚晦。故朱子尝谓伊川语更稳当。而大学章句则从明道说何也。
尝见农岩集。亦有此问。而农岩所答。朱子于论语则用伊川说。于此则却著明道说者。似欲两说俱存。使学者参互而尽其义云。此说不然。朱子释经之法。一依本文语势而为之释。如同一仁释而于论语则曰爱之理心之德。于孟子则曰心之德爱之理者是已。朱子平日定论如彼。而于此却从明道说者。不应无说。愚意则似是因上段文义而为之说。盖曰循物无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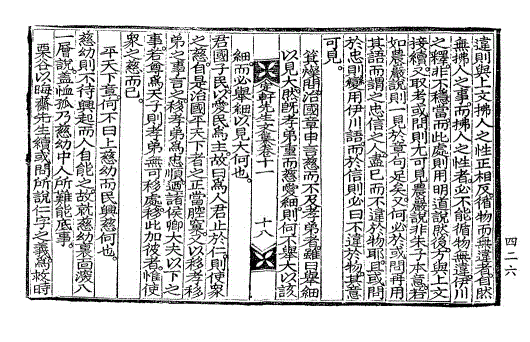 违则与上文拂人之性正相反。循物而无违者。自然无拂人之事。而拂人之性者。必不能循物无违。伊川之释。非不稳当。而此处则用明道说然后。方与上文接续。又取考或问则尤可见农岩说非朱子本意。若如农岩说则一见于章句足矣。又何必于或问再用其语而谓之忠信之人。尽己而不违于物耶。且或问于忠则变用伊川语。而于信则必曰不违于物。其意可见。
违则与上文拂人之性正相反。循物而无违者。自然无拂人之事。而拂人之性者。必不能循物无违。伊川之释。非不稳当。而此处则用明道说然后。方与上文接续。又取考或问则尤可见农岩说非朱子本意。若如农岩说则一见于章句足矣。又何必于或问再用其语而谓之忠信之人。尽己而不违于物耶。且或问于忠则变用伊川语。而于信则必曰不违于物。其意可见。箕灿问。治国章申言慈而不及孝弟者。虽曰举细以见大。然既孝弟重而慈爱细。则何不举大以该细。而必举细以见大何也。
君国子民。以爱民为主。故曰为人君止于仁。则使众之慈。自是治国平天下者之正当腔窠。又以移孝移弟之事言之。移孝弟为忠顺。乃诸侯卿大夫以下之事。若尊为天子则孝弟无可移处。移此加彼者。惟使众之慈而已。
平天下章。何不曰上慈幼而民兴慈何也。
慈幼则不待兴起而人自能之。故就慈幼里面深入一层说。盖恤孤乃慈幼中人所难能底事。
栗谷以晦斋先生续或问所说仁字之义。为救时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7H 页
 悯俗之语。而非传文本意。又谓传文言仁只是带去说。未知此说如何。
悯俗之语。而非传文本意。又谓传文言仁只是带去说。未知此说如何。聚会传文中所及仁字诸处而观之。则决不是偶然带去说。续或问中所敷衍仁字之义。明鬯剀切。深得传者之意。恐未可轻议。为人君止于仁。故治平章数数拈出仁字。尝见屏谷集说此仁字。约而尽。可检看也。
讲未毕。日已曛矣。将罢会。官曰吾之此来。无一事强意。而惟今日此会。犹足以偿雁门之踦。然以日力之不足。未得极意讲讨而罢。极为怅然。如或继此而又图一番会集。以摅今日未尽底蕴则如何。佥曰诺。不敢请固所愿。官曰未相见时。须教有满肚疑难。然后相对庶几有相难之益。佥贤如欲更续此会。则豫定将讲之书。就此一书熟读精究。各各抄出合疑之端。以待他日相见。而慎勿临时凑合。徒为观听之美幸甚。